第一节 刘萨诃的生平及其信仰
| 内容出处: |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952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刘萨诃的生平及其信仰 |
| 分类号: | B949 |
| 页数: | 18 |
| 页码: | 9-26 |
| 摘要: | 本文记述永昌县刘萨诃的生平介绍及其瑞像的这种独特的信仰由一个地方性的信仰逐渐开始向全国流传,瑞相寺也籍着隋炀帝的布施,由原来规模较小的寺院变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 |
| 关键词: | 永昌县 刘萨诃 信仰 |
内容
圣容寺建寺及番禾瑞像的诞生缘起于刘萨诃西行求法时在凉州番禾县所作的“授记”,因此要了解圣容寺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刘萨诃的生平,特别是刘萨诃在番禾县预言后世将有瑞像出现的史实与传说。
刘萨诃,或称萨荷、萨何、窣(读音“苏”)和、萨河、摩诃等,出家以后法名释慧达,其事迹在正史和佛教典籍中都有收录,相关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如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宝唱的《名僧传》,齐王琰的《冥祥记》,姚思廉《梁书》,南山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下简称为“三宝录”)、《道宣律师感通录》(以下简称为“道宣录”)、《释迦方志》,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以及《永昌县志》等等古籍中都记载了与其相关的事迹。
典籍中多记载刘萨诃为稽胡族,或者叫步落稽。关于这个稽胡族,周一良、唐长孺和林幹等诸位先生有考。实际上,稽胡族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包含了匈奴人后裔、西域胡人以及一些当地土人的“杂胡”,①与匈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点从刘萨诃的姓氏亦可看出,刘氏、乔氏、呼延氏和郝氏等姓氏为匈奴之大姓,尤以刘氏为多,刘萨诃又出生于世家大族,故其主要的民族成分应当是匈奴族。南北朝时稽胡族主要居住和活动于并州及周围的山区,即今山西西部吕梁、陕北及内蒙南部一带黄土高原的山谷中,以射猎、游牧和简单的农耕生产为业,可能是地理封闭或其他原因所致,其整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相对比较落后。唐初的文献中尚能见到零星的有关稽胡族的记载,至中唐以后不见于史书,可能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与刘萨诃相关的文字记载,出现时代最早的应属南朝齐王琰的《冥祥记》,梁慧皎的《高僧传》则出现稍晚。《冥祥记》成书于梁初,王琰则生于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前后,后仕于齐、梁间,虽未出家为僧,但幼年时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而成为佛教弟子,曾游历于交趾、峡表、江都等地,南齐建元元年(479年)之际回到京师。他在书中自称幼年跟从贤法师学习时,得到一尊观世音金像。据其在序言中说,此观音金像能“放光照三尺许,金辉秀起,焕然夺目”;自王琰得到此像以后,“瑞验之发,多自是兴”。从其自述和成书的情况来看,《冥祥记》中未免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不过《冥祥记》成书的时间距后来刘萨诃番禾县望御谷“授记”的时间却是最近的。先来看《冥祥记》,其概要如下: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向西北行。俄见两沙门,谓荷,“汝识我不?”荷答:“不识。”沙门曰:“今宜归命释迦文佛”俄而忽见金色,晖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左右并曰:观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礼。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
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谓荷曰:“汝受轻,罪,又得还生,福力所扶。而今以后,复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见故身,意不欲还。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稣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①
《冥祥记》中记载的这一段文字,使得我们可以得知时人对刘萨诃的一些认识:并州西河离石人,即今山西吕梁地区及陕北一带的人。出家为僧之前可能是军卒,喜好田猎,从未听说过有佛法之事。三十一岁时得了暴病却没有死,七日后苏醒。醒来以后就说了一些他在地狱冥游时的经历,诸如受到观世音点化,又因襄阳杀生射鹿而在来世遭受汤镬之刑一类的故事,之后出家,法名释慧达。出家后刘萨诃又去了江东、许昌等地游化,太元末时尚知其在京师,再往后就不知其踪迹了。
王琰关于刘萨诃的记述颇具神话色彩,还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过刘萨诃出家之前和因何出家。首先是确有刘萨诃其人,而且已颇具名气,特别是他暴病之后七日而苏的故事,当时可能流传甚广,否则王琰亦不会在书中列其事迹。刘萨诃出家时已三十一岁,据此可推算其至少生于366年以前,令人费解的是之后这样一位当世名僧就不知所终,杳无音信了,尽管此时正值刘萨诃游化弘法的兴盛期。
梁慧皎的《高僧传》成书较《冥祥记》稍晚,其中也收录了刘萨诃的事迹。《高僧传》所载记事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截止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年),①慧皎本人则卒于梁承圣三年(554年)。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说“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②慧皎乃佛教史家,撰书之立意与方法在此一目了然,又考据详实,删繁补阙,故此书历来为诸家看重。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有关刘萨诃的文字记载,慧皎的记述无疑是相对更为可信的。
《高僧传》卷第十三兴福篇“晋并州竺慧达”载:
③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域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313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滬渎口(慧)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尽夜虔礼,未尝暂废。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鄮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蹠。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慧)达东西观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厉,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此处较王琰所记多出了刘萨诃于晋宁康中到京师建康和鄮县等地礼长干寺、拜阿育王塔像等等“屡表征验”的事迹,且刘萨诃暴病而死以后,只用“备见地域苦报”来一笔带过其在地狱冥游时离奇繁复的经历,叙述了一些其在江东吴松、鄮县等地的礼拜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慧皎的这段记述显示出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前后时间跨度很长,至少自西晋建兴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至东晋宁康中时几乎有增无减,其后仍然“东西观礼,终年无改”。在对刘萨诃是否到过河西走廊番禾县并做“授记”一事,尚丽新等先生的观点,①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刘萨诃出现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所历的时间又跨越了三个世纪,而一个人的寿命毫无疑问没有那么长。还需要注意的是,刘萨诃在各地游化时所作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礼忏,甚至“唯以礼忏为先”很明显这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冥祥记》中并未过,多提及刘萨诃礼忏一事,而是更多的描述了其在地狱中遭遇的各种经历,诚然这是刘萨诃在阳世间做了杀生、射猎等种种“恶事”所致,“业力”深重,有因则必有果报。而到了慧皎这里,刘萨诃主要的活动儿乎就是“礼拜悔过,以忏先罪”了。礼拜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即刘萨诃于会稽鄮县(今宁波鄞州区)发现了阿育王塔,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阿育王塔的记载。此后阿育王塔及对刘萨诃本人的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广泛传播,现存的刘萨诃及阿育王塔的文物古迹也存有不少,遍及浙江(图二)①、上海、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图三)②、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另日本也存有不少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是宋代以后的小型金银或铜质塔,源于宋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模仿阿育王营造八万四千塔之事,建造了众多小型阿育王塔,因其多为金铜制作,又叫做金涂塔,此不在本文所述之范围,兹不赘述。但需注意的是,刘萨诃在江左、东南沿海一带,与阿育王塔一起为人们所崇拜,影响很大。刘萨诃礼拜的活动在以后的文献中也多次出现,并且仍然是刘萨诃所作的主要的佛事活动。梁史的编修,后又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受命编修,至大业二年(606年)去世时尚未及成书,姚思廉继其父编纂。入唐以后,梁史的监修官正是唐代名臣魏征,姚思廉又受命续修,至其去世前一年(636年)方才成书。故从《梁书》的编修经过来看,有关早期的事迹和记载应当比慧皎的《续高僧传》、《三宝录》和释道世的《法苑珠林》等书要早出。
刘萨诃的事情亦见录于《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载:
有西河离石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①
《梁书》的记载与前述文献的记载总体上大同小异。作为正史,从其用语来看似更加贴合实际,如“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等。刘萨诃礼拜的地域范围却扩大了,出现了洛下、齐城等地。但刘萨诃每到一地,首先要做的且最主要做的仍旧是礼拜,以此来洗脱先前所犯的在佛教看来于理不容的种种罪业。又因为刘萨诃“东西观礼”,礼拜活动的范围很大,而且一直不间断的持续了下去,随着这种礼拜范围的逐步扩大,以及刘萨诃受民间和统治阶层的尊崇,使得这种礼拜活动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甚至有可能成为西北地区民间佛事活动中的一套遵循特定制度的佛教仪轨,或者叫作礼拜法。关于这种礼拜法,现藏于英国图书馆的一个编号为斯4494号的敦煌遗书残卷中,保存了一段名为《刘师礼文》的文献,透露了这种礼拜法的一些有关的形态。斯4494号卷尾的题记是:“(西魏)大统十一年乙丑岁(545)五月廿九日写乞(讫),平南寺道养许”,是南北朝西魏时期平南寺的一位叫道养的僧人个人所持有的写卷,方广錩先生将其定名为“道养文本”,并对这幅残卷做了深入研究。首先判定了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刘师”就是“早期中国信仰性佛教的代表人物——刘萨诃”,其后又讨论了《刘师礼文》中反映出的这个礼拜法的形态。为了达到修持者的目的,即要求修持者于特定的月份特定的日子,在特定的时辰,向某个特定的方向礼拜特定的次数,这样礼拜的效果可以灭除特定的罪孽或者减少罪数,如果能坚持三年,则能成道,所得遂愿;①并在《〈刘师礼文〉中礼拜法初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礼拜法可能被组织成为某种佛教仪轨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礼拜法与早期中国道教的礼忏思想和礼忏形式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和道教相关的情况因囿于笔者所限且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此处不再赘述,但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及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
唐初终南山律师道宣在《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等著述中多次提到刘萨诃的事迹,于其事迹也是著录最丰者。《三宝录》撰成于唐麟德元年(664年),《续高僧传》成书则至迟在麟德二年(665年)。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西晋会稽鄮塔缘一”中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并州离石人刘萨何得病死之后见一梵僧,说其罪重应入地狱,因怜悯他无识而放生,让其往洛下、齐城、丹阳、会稽等地寻浮江石像和阿育王塔并精勤礼拜,死后可免下地狱。醒来后改名慧达,遂出家学佛。后至宁波山中掘得灵塔一座,“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①时人认为这就是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并将涌出塔之山命名为阿育王山至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在刘萨诃礼拜出塔之地又修建了塔亭,这也是阿育王寺建寺之始。鄮县阿育寺又名阿育王广利寺,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宝幢镇,古属会稽郡。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约200年之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将佛祖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每份舍利并造一塔以为供养,在中国共计建有19座舍利塔,这19座塔中因刘萨诃的礼拜活动而建造的塔寺就占了两座,即会稽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干寺塔。
由此可见,刘萨诃是被寄予了厚望的,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能完成好观音交予的种种“任务”,不仅可免自己死后下地狱遭受诸般痛苦惩罚,又能广弘佛法,在自己觉悟成佛的同时引导人们都能觉悟,还能受到人们的尊崇礼敬,岂不是一举多得!自刘萨诃甫一登场,就能感出佛教标志性的建筑物——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于寺塔等等,这样的大事之于佛教来说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又因为有死而复生后出家为僧的神奇经历,他在江东各地礼拜佛塔的事迹也逐渐的被增益、神化,原本比较简单的佛事活动又被附会添加了一些灵验的事迹,也使得刘萨诃的生平事迹愈来愈神奇,神话色彩愈加浓厚,直至最后成为了佛教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之一。那么,与此相关的传说自然更多的被附会到刘萨诃的身上,因为自一开始他就是“成大事者”,就有能感通神迹的本领,并且广为人们所熟知,相互传诵,深信不疑,直至最后形成一种信仰。不过此时对刘萨诃的信仰更多的凝结在他个人的身上,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基于对其个人的神奇经历和依附于佛教的感通事迹而言,或可称其为“刘萨诃信仰”。既然他具有能“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在这之后能预言佛像诞生或者其它神异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续高僧传》“感通篇”中记载了刘萨诃的生平:
释慧达,姓刘,名窣(音“苏”)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间,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慧)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①
道宣在此对关于刘萨诃的生平事迹与先前出现的相关记载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其籍贯变成了咸阳东北的三城定阳,而之前大多记载其为西河离石人;其本人“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家境非常殷实,其后又在襄阳充任一边境小吏。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少、兵痞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不过除了“乐行射猎”以外,没有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他到底干了什么恶事,或者说表达不清,以致于众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低。那么亦有可能道宣在记录此事的时候有意为之,这就使得前后差别显得更大。佛教既要广弘佛法,首先就要证明其“法力”有多么高超,连这种恶少、兵痞一类都能为其所度化,于普通人来讲岂不是更具吸引力。后文又记载:
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慧)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520年)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间,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建德初(572—578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命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575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581—600年)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初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延、丹、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①
道宣虽然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我们还是极需要做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的。同为道宣所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续高僧传》内容也大致相同,此处以《续高僧传》所记的内容为主。通过道宣的记述看出,刘萨诃预言雷震山裂,瑞像现世,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世亦有屡次应验。特别是隋炀帝自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宾客之后,听说了当地这尊佛像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和能预言国之丧乱的功能,专程至瑞相寺礼拜,并亲自书写题名,将“瑞相寺”改名为“感通寺”,让随行的画师图画模写瑞像之形象,分发各地,下令全国的寺院以为供奉。借着最高统治者隋炀帝的尊崇和推广,各地的寺院纷纷供养此像。至此,瑞像的这种独特的信仰由一个地方性的信仰逐渐开始向全国流传,瑞相寺也籍着隋炀帝的布施,由原来规模较小的寺院变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原来不甚知名的、地方性的寺院也日渐声隆,堪称河西名寺,隋炀帝于瑞像信仰的传播及圣容寺的营修建造功不可没。散布在全国各地石窟寺中的番禾瑞像的各种形象,有石雕者,有泥塑者,或图画的,或用绢帛刺绣的①,这些形象也多从炀帝之后雕刻造作。反之,瑞像那种独特的形象通过造像等方式的传播,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传说又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神化了。人们在谈到刘萨诃或是在供奉番禾瑞像时,都能由此而联想到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一系列不平凡的故事经历,二者间“相得益彰”,促使他们各自的信众和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增多增大。
其后有关刘萨诃的文字又分别见载于唐初姚思廉的《梁书》和南山律师道宣的几种著作中。《梁书》共五十六卷,实际上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在六世纪中期至七世纪三十年代相继编撰的,历陈、隋、唐三代而成。姚察在陈初曾参与
刘萨诃,或称萨荷、萨何、窣(读音“苏”)和、萨河、摩诃等,出家以后法名释慧达,其事迹在正史和佛教典籍中都有收录,相关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如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宝唱的《名僧传》,齐王琰的《冥祥记》,姚思廉《梁书》,南山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下简称为“三宝录”)、《道宣律师感通录》(以下简称为“道宣录”)、《释迦方志》,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以及《永昌县志》等等古籍中都记载了与其相关的事迹。
典籍中多记载刘萨诃为稽胡族,或者叫步落稽。关于这个稽胡族,周一良、唐长孺和林幹等诸位先生有考。实际上,稽胡族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包含了匈奴人后裔、西域胡人以及一些当地土人的“杂胡”,①与匈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点从刘萨诃的姓氏亦可看出,刘氏、乔氏、呼延氏和郝氏等姓氏为匈奴之大姓,尤以刘氏为多,刘萨诃又出生于世家大族,故其主要的民族成分应当是匈奴族。南北朝时稽胡族主要居住和活动于并州及周围的山区,即今山西西部吕梁、陕北及内蒙南部一带黄土高原的山谷中,以射猎、游牧和简单的农耕生产为业,可能是地理封闭或其他原因所致,其整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相对比较落后。唐初的文献中尚能见到零星的有关稽胡族的记载,至中唐以后不见于史书,可能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与刘萨诃相关的文字记载,出现时代最早的应属南朝齐王琰的《冥祥记》,梁慧皎的《高僧传》则出现稍晚。《冥祥记》成书于梁初,王琰则生于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前后,后仕于齐、梁间,虽未出家为僧,但幼年时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而成为佛教弟子,曾游历于交趾、峡表、江都等地,南齐建元元年(479年)之际回到京师。他在书中自称幼年跟从贤法师学习时,得到一尊观世音金像。据其在序言中说,此观音金像能“放光照三尺许,金辉秀起,焕然夺目”;自王琰得到此像以后,“瑞验之发,多自是兴”。从其自述和成书的情况来看,《冥祥记》中未免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不过《冥祥记》成书的时间距后来刘萨诃番禾县望御谷“授记”的时间却是最近的。先来看《冥祥记》,其概要如下: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向西北行。俄见两沙门,谓荷,“汝识我不?”荷答:“不识。”沙门曰:“今宜归命释迦文佛”俄而忽见金色,晖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左右并曰:观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礼。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
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谓荷曰:“汝受轻,罪,又得还生,福力所扶。而今以后,复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见故身,意不欲还。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稣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①
《冥祥记》中记载的这一段文字,使得我们可以得知时人对刘萨诃的一些认识:并州西河离石人,即今山西吕梁地区及陕北一带的人。出家为僧之前可能是军卒,喜好田猎,从未听说过有佛法之事。三十一岁时得了暴病却没有死,七日后苏醒。醒来以后就说了一些他在地狱冥游时的经历,诸如受到观世音点化,又因襄阳杀生射鹿而在来世遭受汤镬之刑一类的故事,之后出家,法名释慧达。出家后刘萨诃又去了江东、许昌等地游化,太元末时尚知其在京师,再往后就不知其踪迹了。
王琰关于刘萨诃的记述颇具神话色彩,还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过刘萨诃出家之前和因何出家。首先是确有刘萨诃其人,而且已颇具名气,特别是他暴病之后七日而苏的故事,当时可能流传甚广,否则王琰亦不会在书中列其事迹。刘萨诃出家时已三十一岁,据此可推算其至少生于366年以前,令人费解的是之后这样一位当世名僧就不知所终,杳无音信了,尽管此时正值刘萨诃游化弘法的兴盛期。
梁慧皎的《高僧传》成书较《冥祥记》稍晚,其中也收录了刘萨诃的事迹。《高僧传》所载记事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截止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年),①慧皎本人则卒于梁承圣三年(554年)。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说“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②慧皎乃佛教史家,撰书之立意与方法在此一目了然,又考据详实,删繁补阙,故此书历来为诸家看重。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有关刘萨诃的文字记载,慧皎的记述无疑是相对更为可信的。
《高僧传》卷第十三兴福篇“晋并州竺慧达”载:
③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域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313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滬渎口(慧)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尽夜虔礼,未尝暂废。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鄮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蹠。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慧)达东西观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厉,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此处较王琰所记多出了刘萨诃于晋宁康中到京师建康和鄮县等地礼长干寺、拜阿育王塔像等等“屡表征验”的事迹,且刘萨诃暴病而死以后,只用“备见地域苦报”来一笔带过其在地狱冥游时离奇繁复的经历,叙述了一些其在江东吴松、鄮县等地的礼拜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慧皎的这段记述显示出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前后时间跨度很长,至少自西晋建兴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至东晋宁康中时几乎有增无减,其后仍然“东西观礼,终年无改”。在对刘萨诃是否到过河西走廊番禾县并做“授记”一事,尚丽新等先生的观点,①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刘萨诃出现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所历的时间又跨越了三个世纪,而一个人的寿命毫无疑问没有那么长。还需要注意的是,刘萨诃在各地游化时所作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礼忏,甚至“唯以礼忏为先”很明显这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冥祥记》中并未过,多提及刘萨诃礼忏一事,而是更多的描述了其在地狱中遭遇的各种经历,诚然这是刘萨诃在阳世间做了杀生、射猎等种种“恶事”所致,“业力”深重,有因则必有果报。而到了慧皎这里,刘萨诃主要的活动儿乎就是“礼拜悔过,以忏先罪”了。礼拜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即刘萨诃于会稽鄮县(今宁波鄞州区)发现了阿育王塔,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阿育王塔的记载。此后阿育王塔及对刘萨诃本人的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广泛传播,现存的刘萨诃及阿育王塔的文物古迹也存有不少,遍及浙江(图二)①、上海、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图三)②、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另日本也存有不少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是宋代以后的小型金银或铜质塔,源于宋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模仿阿育王营造八万四千塔之事,建造了众多小型阿育王塔,因其多为金铜制作,又叫做金涂塔,此不在本文所述之范围,兹不赘述。但需注意的是,刘萨诃在江左、东南沿海一带,与阿育王塔一起为人们所崇拜,影响很大。刘萨诃礼拜的活动在以后的文献中也多次出现,并且仍然是刘萨诃所作的主要的佛事活动。梁史的编修,后又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受命编修,至大业二年(606年)去世时尚未及成书,姚思廉继其父编纂。入唐以后,梁史的监修官正是唐代名臣魏征,姚思廉又受命续修,至其去世前一年(636年)方才成书。故从《梁书》的编修经过来看,有关早期的事迹和记载应当比慧皎的《续高僧传》、《三宝录》和释道世的《法苑珠林》等书要早出。
刘萨诃的事情亦见录于《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载:
有西河离石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①
《梁书》的记载与前述文献的记载总体上大同小异。作为正史,从其用语来看似更加贴合实际,如“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等。刘萨诃礼拜的地域范围却扩大了,出现了洛下、齐城等地。但刘萨诃每到一地,首先要做的且最主要做的仍旧是礼拜,以此来洗脱先前所犯的在佛教看来于理不容的种种罪业。又因为刘萨诃“东西观礼”,礼拜活动的范围很大,而且一直不间断的持续了下去,随着这种礼拜范围的逐步扩大,以及刘萨诃受民间和统治阶层的尊崇,使得这种礼拜活动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甚至有可能成为西北地区民间佛事活动中的一套遵循特定制度的佛教仪轨,或者叫作礼拜法。关于这种礼拜法,现藏于英国图书馆的一个编号为斯4494号的敦煌遗书残卷中,保存了一段名为《刘师礼文》的文献,透露了这种礼拜法的一些有关的形态。斯4494号卷尾的题记是:“(西魏)大统十一年乙丑岁(545)五月廿九日写乞(讫),平南寺道养许”,是南北朝西魏时期平南寺的一位叫道养的僧人个人所持有的写卷,方广錩先生将其定名为“道养文本”,并对这幅残卷做了深入研究。首先判定了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刘师”就是“早期中国信仰性佛教的代表人物——刘萨诃”,其后又讨论了《刘师礼文》中反映出的这个礼拜法的形态。为了达到修持者的目的,即要求修持者于特定的月份特定的日子,在特定的时辰,向某个特定的方向礼拜特定的次数,这样礼拜的效果可以灭除特定的罪孽或者减少罪数,如果能坚持三年,则能成道,所得遂愿;①并在《〈刘师礼文〉中礼拜法初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礼拜法可能被组织成为某种佛教仪轨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礼拜法与早期中国道教的礼忏思想和礼忏形式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和道教相关的情况因囿于笔者所限且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此处不再赘述,但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及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
唐初终南山律师道宣在《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等著述中多次提到刘萨诃的事迹,于其事迹也是著录最丰者。《三宝录》撰成于唐麟德元年(664年),《续高僧传》成书则至迟在麟德二年(665年)。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西晋会稽鄮塔缘一”中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并州离石人刘萨何得病死之后见一梵僧,说其罪重应入地狱,因怜悯他无识而放生,让其往洛下、齐城、丹阳、会稽等地寻浮江石像和阿育王塔并精勤礼拜,死后可免下地狱。醒来后改名慧达,遂出家学佛。后至宁波山中掘得灵塔一座,“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①时人认为这就是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并将涌出塔之山命名为阿育王山至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在刘萨诃礼拜出塔之地又修建了塔亭,这也是阿育王寺建寺之始。鄮县阿育寺又名阿育王广利寺,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宝幢镇,古属会稽郡。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约200年之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将佛祖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每份舍利并造一塔以为供养,在中国共计建有19座舍利塔,这19座塔中因刘萨诃的礼拜活动而建造的塔寺就占了两座,即会稽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干寺塔。
由此可见,刘萨诃是被寄予了厚望的,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能完成好观音交予的种种“任务”,不仅可免自己死后下地狱遭受诸般痛苦惩罚,又能广弘佛法,在自己觉悟成佛的同时引导人们都能觉悟,还能受到人们的尊崇礼敬,岂不是一举多得!自刘萨诃甫一登场,就能感出佛教标志性的建筑物——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于寺塔等等,这样的大事之于佛教来说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又因为有死而复生后出家为僧的神奇经历,他在江东各地礼拜佛塔的事迹也逐渐的被增益、神化,原本比较简单的佛事活动又被附会添加了一些灵验的事迹,也使得刘萨诃的生平事迹愈来愈神奇,神话色彩愈加浓厚,直至最后成为了佛教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之一。那么,与此相关的传说自然更多的被附会到刘萨诃的身上,因为自一开始他就是“成大事者”,就有能感通神迹的本领,并且广为人们所熟知,相互传诵,深信不疑,直至最后形成一种信仰。不过此时对刘萨诃的信仰更多的凝结在他个人的身上,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基于对其个人的神奇经历和依附于佛教的感通事迹而言,或可称其为“刘萨诃信仰”。既然他具有能“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在这之后能预言佛像诞生或者其它神异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续高僧传》“感通篇”中记载了刘萨诃的生平:
释慧达,姓刘,名窣(音“苏”)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间,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慧)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①
道宣在此对关于刘萨诃的生平事迹与先前出现的相关记载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其籍贯变成了咸阳东北的三城定阳,而之前大多记载其为西河离石人;其本人“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家境非常殷实,其后又在襄阳充任一边境小吏。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少、兵痞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不过除了“乐行射猎”以外,没有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他到底干了什么恶事,或者说表达不清,以致于众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低。那么亦有可能道宣在记录此事的时候有意为之,这就使得前后差别显得更大。佛教既要广弘佛法,首先就要证明其“法力”有多么高超,连这种恶少、兵痞一类都能为其所度化,于普通人来讲岂不是更具吸引力。后文又记载:
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慧)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520年)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间,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建德初(572—578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命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575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581—600年)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初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延、丹、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①
道宣虽然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我们还是极需要做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的。同为道宣所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续高僧传》内容也大致相同,此处以《续高僧传》所记的内容为主。通过道宣的记述看出,刘萨诃预言雷震山裂,瑞像现世,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世亦有屡次应验。特别是隋炀帝自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宾客之后,听说了当地这尊佛像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和能预言国之丧乱的功能,专程至瑞相寺礼拜,并亲自书写题名,将“瑞相寺”改名为“感通寺”,让随行的画师图画模写瑞像之形象,分发各地,下令全国的寺院以为供奉。借着最高统治者隋炀帝的尊崇和推广,各地的寺院纷纷供养此像。至此,瑞像的这种独特的信仰由一个地方性的信仰逐渐开始向全国流传,瑞相寺也籍着隋炀帝的布施,由原来规模较小的寺院变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原来不甚知名的、地方性的寺院也日渐声隆,堪称河西名寺,隋炀帝于瑞像信仰的传播及圣容寺的营修建造功不可没。散布在全国各地石窟寺中的番禾瑞像的各种形象,有石雕者,有泥塑者,或图画的,或用绢帛刺绣的①,这些形象也多从炀帝之后雕刻造作。反之,瑞像那种独特的形象通过造像等方式的传播,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传说又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神化了。人们在谈到刘萨诃或是在供奉番禾瑞像时,都能由此而联想到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一系列不平凡的故事经历,二者间“相得益彰”,促使他们各自的信众和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增多增大。
其后有关刘萨诃的文字又分别见载于唐初姚思廉的《梁书》和南山律师道宣的几种著作中。《梁书》共五十六卷,实际上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在六世纪中期至七世纪三十年代相继编撰的,历陈、隋、唐三代而成。姚察在陈初曾参与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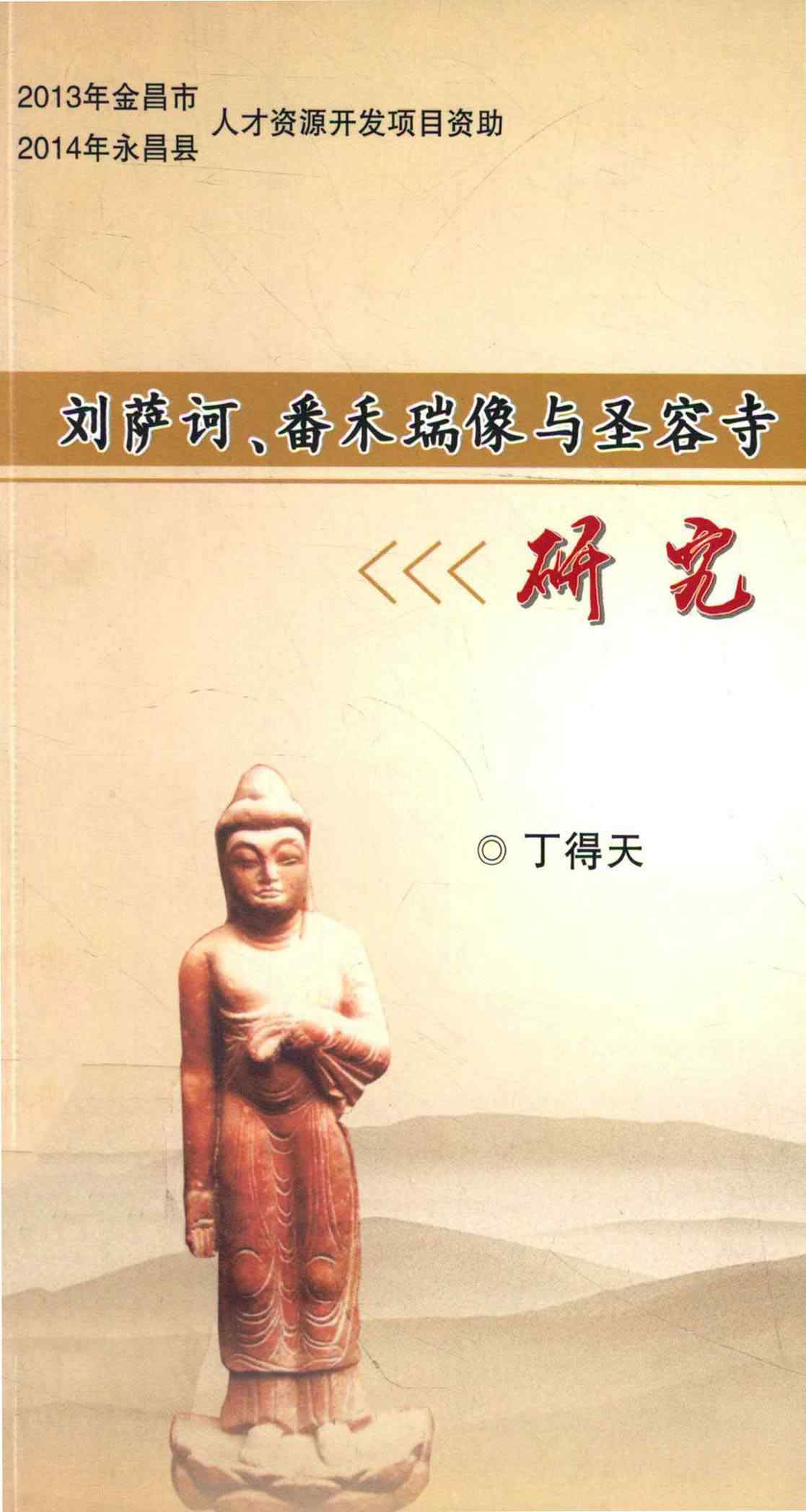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介绍了刘萨诃的生平以及番禾瑞像和圣容寺的情况,对望御谷及周边的佛教遗迹做了全面的调查,著录了金昌市境内散见的佛教石窟寺遗迹以及清代《永昌县志》所记载的古寺。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