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
| 内容出处: |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951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 |
| 分类号: | K235;K879.4; K928.75 |
| 页数: | 41 |
| 页码: | 7-47 |
| 摘要: | 本章记述永昌县刘萨诃的生平及其信仰、番禾瑞像、其他代表性造像及文物资料。 |
| 关键词: | 永昌县 刘萨诃 圣容寺 |
内容
圣容寺当地民间俗称为后大寺,坐落于今甘肃永昌县城北,约11公里处的金川西村望御谷。圣容寺在河西古寺中堪称名寺,其名称亦经历了前后三次变化,北周初建时名为瑞像寺,隋炀帝改名为感通寺,吐蕃、西夏以后名为圣容寺。早期兴建石窟寺庙,一般会选择僻静的山崖河谷,以利于僧人参禅观想,而望御谷就具备了这种佛教所需的良好的自然条件。望御谷大致呈东西走向,全长约十余公里,两山最窄的峡口处仅有40多米。谷内蜿蜒曲折,明长城即矗立于谷底北侧,依山麓绵亘一直向西出谷,过绣花庙、定羌庙接张掖山丹县。谷中泉水自西向东流经山谷,过圣容寺门前,再汇入金川,其水势颇大(图一)。①古时谷中寺田、农田皆可以此水做为灌溉之用两侧山崖高耸,峭壁林立,唯有峡谷中间沿溪一条大道,路途平坦,可通车马,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过境永昌的重要通道。圣容寺即建在望御谷西端出口处的虎头山南麓,面对武当山,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泉水曲绕寺前,四周林木成荫。清永昌籍进士南济汉先生编修的嘉庆二十一年本《永昌县志》中,载有他游览后大寺时所作的题为《后大寺》的诗一首:
一线边垣达玉关,半渠流水入萧湾。①
红尘不到幽深处,绀宇常浮杏霭间。
佛后洞中仍礼佛,山前寺外更观山。
当年胜地时防虏,花木于今总是闲。
在河西干旱砂碛之地寻得此幽深清静的场所,实属不易,正是佛教弟子出家修行的理想之地。
第一节 刘萨诃的生平及其信仰
圣容寺建寺及番禾瑞像的诞生缘起于刘萨诃西行求法时在凉州番禾县所作的“授记”,因此要了解圣容寺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刘萨诃的生平,特别是刘萨诃在番禾县预言后世将有瑞像出现的史实与传说。
刘萨诃,或称萨荷、萨何、窣(读音“苏”)和、萨河、摩诃等,出家以后法名释慧达,其事迹在正史和佛教典籍中都有收录,相关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如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宝唱的《名僧传》,齐王琰的《冥祥记》,姚思廉《梁书》,南山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下简称为“三宝录”)、《道宣律师感通录》(以下简称为“道宣录”)、《释迦方志》,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以及《永昌县志》等等古籍中都记载了与其相关的事迹。
典籍中多记载刘萨诃为稽胡族,或者叫步落稽。关于这个稽胡族,周一良、唐长孺和林幹等诸位先生有考。实际上,稽胡族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包含了匈奴人后裔、西域胡人以及一些当地土人的“杂胡”,①与匈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点从刘萨诃的姓氏亦可看出,刘氏、乔氏、呼延氏和郝氏等姓氏为匈奴之大姓,尤以刘氏为多,刘萨诃又出生于世家大族,故其主要的民族成分应当是匈奴族。南北朝时稽胡族主要居住和活动于并州及周围的山区,即今山西西部吕梁、陕北及内蒙南部一带黄土高原的山谷中,以射猎、游牧和简单的农耕生产为业,可能是地理封闭或其他原因所致,其整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相对比较落后。唐初的文献中尚能见到零星的有关稽胡族的记载,至中唐以后不见于史书,可能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与刘萨诃相关的文字记载,出现时代最早的应属南朝齐王琰的《冥祥记》,梁慧皎的《高僧传》则出现稍晚。《冥祥记》成书于梁初,王琰则生于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前后,后仕于齐、梁间,虽未出家为僧,但幼年时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而成为佛教弟子,曾游历于交趾、峡表、江都等地,南齐建元元年(479年)之际回到京师。他在书中自称幼年跟从贤法师学习时,得到一尊观世音金像。据其在序言中说,此观音金像能“放光照三尺许,金辉秀起,焕然夺目”;自王琰得到此像以后,“瑞验之发,多自是兴”。从其自述和成书的情况来看,《冥祥记》中未免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不过《冥祥记》成书的时间距后来刘萨诃番禾县望御谷“授记”的时间却是最近的。先来看《冥祥记》,其概要如下: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向西北行。俄见两沙门,谓荷,“汝识我不?”荷答:“不识。”沙门曰:“今宜归命释迦文佛”俄而忽见金色,晖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左右并曰:观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礼。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
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谓荷曰:“汝受轻,罪,又得还生,福力所扶。而今以后,复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见故身,意不欲还。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稣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①
《冥祥记》中记载的这一段文字,使得我们可以得知时人对刘萨诃的一些认识:并州西河离石人,即今山西吕梁地区及陕北一带的人。出家为僧之前可能是军卒,喜好田猎,从未听说过有佛法之事。三十一岁时得了暴病却没有死,七日后苏醒。醒来以后就说了一些他在地狱冥游时的经历,诸如受到观世音点化,又因襄阳杀生射鹿而在来世遭受汤镬之刑一类的故事,之后出家,法名释慧达。出家后刘萨诃又去了江东、许昌等地游化,太元末时尚知其在京师,再往后就不知其踪迹了。
王琰关于刘萨诃的记述颇具神话色彩,还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过刘萨诃出家之前和因何出家。首先是确有刘萨诃其人,而且已颇具名气,特别是他暴病之后七日而苏的故事,当时可能流传甚广,否则王琰亦不会在书中列其事迹。刘萨诃出家时已三十一岁,据此可推算其至少生于366年以前,令人费解的是之后这样一位当世名僧就不知所终,杳无音信了,尽管此时正值刘萨诃游化弘法的兴盛期。
梁慧皎的《高僧传》成书较《冥祥记》稍晚,其中也收录了刘萨诃的事迹。《高僧传》所载记事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截止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年),①慧皎本人则卒于梁承圣三年(554年)。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说“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②慧皎乃佛教史家,撰书之立意与方法在此一目了然,又考据详实,删繁补阙,故此书历来为诸家看重。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有关刘萨诃的文字记载,慧皎的记述无疑是相对更为可信的。
《高僧传》卷第十三兴福篇“晋并州竺慧达”载:③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域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313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滬渎口(慧)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尽夜虔礼,未尝暂废。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鄮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蹠。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慧)达东西观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厉,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此处较王琰所记多出了刘萨诃于晋宁康中到京师建康和鄮县等地礼长干寺、拜阿育王塔像等等“屡表征验”的事迹,且刘萨诃暴病而死以后,只用“备见地域苦报”来一笔带过其在地狱冥游时离奇繁复的经历,叙述了一些其在江东吴松、鄮县等地的礼拜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慧皎的这段记述显示出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前后时间跨度很长,至少自西晋建兴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至东晋宁康中时几乎有增无减,其后仍然“东西观礼,终年无改”。在对刘萨诃是否到过河西走廊番禾县并做“授记”一事,尚丽新等先生的观点,①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刘萨诃出现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所历的时间又跨越了三个世纪,而一个人的寿命毫无疑问没有那么长。还需要注意的是,刘萨诃在各地游化时所作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礼忏,甚至“唯以礼忏为先”很明显这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冥祥记》中并未过,多提及刘萨诃礼忏一事,而是更多的描述了其在地狱中遭遇的各种经历,诚然这是刘萨诃在阳世间做了杀生、射猎等种种“恶事”所致,“业力”深重,有因则必有果报。而到了慧皎这里,刘萨诃主要的活动儿乎就是“礼拜悔过,以忏先罪”了。礼拜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即刘萨诃于会稽鄮县(今宁波鄞州区)发现了阿育王塔,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阿育王塔的记载。此后阿育王塔及对刘萨诃本人的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广泛传播,现存的刘萨诃及阿育王塔的文物古迹也存有不少,遍及浙江(图二)①、上海、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图三)②、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另日本也存有不少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是宋代以后的小型金银或铜质塔,源于宋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模仿阿育王营造八万四千塔之事,建造了众多小型阿育王塔,因其多为金铜制作,又叫做金涂塔,此不在本文所述之范围,兹不赘述。但需注意的是,刘萨诃在江左、东南沿海一带,与阿育王塔一起为人们所崇拜,影响很大。刘萨诃礼拜的活动在以后的文献中也多次出现,并且仍然是刘萨诃所作的主要的佛事活动。
其后有关刘萨诃的文字又分别见载于唐初姚思廉的《梁书》和南山律师道宣的几种著作中。《梁书》共五十六卷,实际上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在六世纪中期至七世纪三十年代相继编撰的,历陈、隋、唐三代而成。姚察在陈初曾参与
①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银质阿育王塔及舍利瓶照片。梁史的编修,后又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受命编修,至大业二年(606年)去世时尚未及成书,姚思廉继其父编纂。入唐以后,梁史的监修官正是唐代名臣魏征,姚思廉又受命续修,至其去世前一年(636年)方才成书。故从《梁书》的编修经过来看,有关早期的事迹和记载应当比慧皎的《续高僧传》、《三宝录》和释道世的《法苑珠林》等书要早出。
刘萨诃的事情亦见录于《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载:
有西河离石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①
《梁书》的记载与前述文献的记载总体上大同小异。作为正史,从其用语来看似更加贴合实际,如“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等。刘萨诃礼拜的地域范围却扩大了,出现了洛下、齐城等地。但刘萨诃每到一地,首先要做的且最主要做的仍旧是礼拜,以此来洗脱先前所犯的在佛教看来于理不容的种种罪业。又因为刘萨诃“东西观礼”,礼拜活动的范围很大,而且一直不间断的持续了下去,随着这种礼拜范围的逐步扩大,以及刘萨诃受民间和统治阶层的尊崇,使得这种礼拜活动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甚至有可能成为西北地区民间佛事活动中的一套遵循特定制度的佛教仪轨,或者叫作礼拜法。关于这种礼拜法,现藏于英国图书馆的一个编号为斯4494号的敦煌遗书残卷中,保存了一段名为《刘师礼文》的文献,透露了这种礼拜法的一些有关的形态。斯4494号卷尾的题记是:“(西魏)大统十一年乙丑岁(545)五月廿九日写乞(讫),平南寺道养许”,是南北朝西魏时期平南寺的一位叫道养的僧人个人所持有的写卷,方广錩先生将其定名为“道养文本”,并对这幅残卷做了深入研究。首先判定了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刘师”就是“早期中国信仰性佛教的代表人物——刘萨诃”,其后又讨论了《刘师礼文》中反映出的这个礼拜法的形态。为了达到修持者的目的,即要求修持者于特定的月份特定的日子,在特定的时辰,向某个特定的方向礼拜特定的次数,这样礼拜的效果可以灭除特定的罪孽或者减少罪数,如果能坚持三年,则能成道,所得遂愿;①并在《〈刘师礼文〉中礼拜法初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礼拜法可能被组织成为某种佛教仪轨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礼拜法与早期中国道教的礼忏思想和礼忏形式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和道教相关的情况因囿于笔者所限且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此处不再赘述,但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及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
唐初终南山律师道宣在《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等著述中多次提到刘萨诃的事迹,于其事迹也是著录最丰者。《三宝录》撰成于唐麟德元年(664年),《续高僧传》成书则至迟在麟德二年(665年)。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西晋会稽鄮塔缘一”中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并州离石人刘萨何得病死之后见一梵僧,说其罪重应入地狱,因怜悯他无识而放生,让其往洛下、齐城、丹阳、会稽等地寻浮江石像和阿育王塔并精勤礼拜,死后可免下地狱。醒来后改名慧达,遂出家学佛。后至宁波山中掘得灵塔一座,“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①时人认为这就是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并将涌出塔之山命名为阿育王山至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在刘萨诃礼拜出塔之地又修建了塔亭,这也是阿育王寺建寺之始。鄮县阿育寺又名阿育王广利寺,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宝幢镇,古属会稽郡。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约200年之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将佛祖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每份舍利并造一塔以为供养,在中国共计建有19座舍利塔,这19座塔中因刘萨诃的礼拜活动而建造的塔寺就占了两座,即会稽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干寺塔。
由此可见,刘萨诃是被寄予了厚望的,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能完成好观音交予的种种“任务”,不仅可免自己死后下地狱遭受诸般痛苦惩罚,又能广弘佛法,在自己觉悟成佛的同时引导人们都能觉悟,还能受到人们的尊崇礼敬,岂不是一举多得!自刘萨诃甫一登场,就能感出佛教标志性的建筑物——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于寺塔等等,这样的大事之于佛教来说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又因为有死而复生后出家为僧的神奇经历,他在江东各地礼拜佛塔的事迹也逐渐的被增益、神化,原本比较简单的佛事活动又被附会添加了一些灵验的事迹,也使得刘萨诃的生平事迹愈来愈神奇,神话色彩愈加浓厚,直至最后成为了佛教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之一。那么,与此相关的传说自然更多的被附会到刘萨诃的身上,因为自一开始他就是“成大事者”,就有能感通神迹的本领,并且广为人们所熟知,相互传诵,深信不疑,直至最后形成一种信仰。不过此时对刘萨诃的信仰更多的凝结在他个人的身上,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基于对其个人的神奇经历和依附于佛教的感通事迹而言,或可称其为“刘萨诃信仰”。既然他具有能“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在这之后能预言佛像诞生或者其它神异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续高僧传》“感通篇”中记载了刘萨诃的生平:
释慧达,姓刘,名窣(音“苏”)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间,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慧)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①
道宣在此对关于刘萨诃的生平事迹与先前出现的相关记载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其籍贯变成了咸阳东北的三城定阳,而之前大多记载其为西河离石人;其本人“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家境非常殷实,其后又在襄阳充任一边境小吏。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少、兵痞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不过除了“乐行射猎”以外,没有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他到底干了什么恶事,或者说表达不清,以致于众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低。那么亦有可能道宣在记录此事的时候有意为之,这就使得前后差别显得更大。佛教既要广弘佛法,首先就要证明其“法力”有多么高超,连这种恶少、兵痞一类都能为其所度化,于普通人来讲岂不是更具吸引力。后文又记载:
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慧)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520年)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间,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建德初(572—578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命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575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581—600年)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初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延、丹、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①
道宣虽然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我们还是极需要做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的。同为道宣所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续高僧传》内容也大致相同,此处以《续高僧传》所记的内容为主。通过道宣的记述看出,刘萨诃预言雷震山裂,瑞像现世,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世亦有屡次应验。特别是隋炀帝自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宾客之后,听说了当地这尊佛像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和能预言国之丧乱的功能,专程至瑞相寺礼拜,并亲自书写题名,将“瑞相寺”改名为“感通寺”,让随行的画师图画模写瑞像之形象,分发各地,下令全国的寺院以为供奉。借着最高统治者隋炀帝的尊崇和推广,各地的寺院纷纷供养此像。至此,瑞像的这种独特的信仰由一个地方性的信仰逐渐开始向全国流传,瑞相寺也籍着隋炀帝的布施,由原来规模较小的寺院变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原来不甚知名的、地方性的寺院也日渐声隆,堪称河西名寺,隋炀帝于瑞像信仰的传播及圣容寺的营修建造功不可没。散布在全国各地石窟寺中的番禾瑞像的各种形象,有石雕者,有泥塑者,或图画的,或用绢帛刺绣的①,这些形象也多从炀帝之后雕刻造作。反之,瑞像那种独特的形象通过造像等方式的传播,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传说又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神化了。人们在谈到刘萨诃或是在供奉番禾瑞像时,都能由此而联想到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一系列不平凡的故事经历,二者间“相得益彰”,促使他们各自的信众和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增多增大。
第二节 番禾瑞像
一、番禾瑞像与望御谷
番禾瑞像既诞生于番禾县望御谷,番禾县和望御谷的关系就需要做一简单的了解,尤其是望御谷的情况以前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现在看来,望御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番禾瑞像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番禾一作“番和”,初为汉置县,名番和,魏晋因之,其故治在今永昌县西。望御谷之名最初不知从何而来,亦不见于史册,最初或叫做“御山”。番禾县自西汉置郡以来,一直沿用到晚唐五代宋时期,凡历700多年,期间因为朝代的更替和战争的缘故,有几次暂废和改称,尽管时间都较为短暂,但是番禾郡的故治并未随之而发生变化。从一些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①,番禾古城的规模之大在河西地区也是比较少见的。有说番禾县故址在今焦家庄乡南约一公里处,有说在今之南、北古城一带,皆因没有充足的史料、考古遗迹加以佐证而未有定论,尚待详考,因这一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不再展开。但可以确定的是,不论番禾古城的故址在焦家庄乡南或是南北古城一带,其地理方位均在永昌县西,这就与道宣所记载的刘萨诃向东北方向之望御谷“遥礼”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道宣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河西走廊一带。而位于今永昌县城北部的望御谷,也不过就是一个偏僻的峡谷而已,番禾县城就处在望御谷的西南方向,并且中间还隔着武当山,二者相距十几里地,道宣和之前大多数的作者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其记载却丝毫不差。类似于此种夹杂着道听途说式的有关望御谷的记载,说明望御谷在当时就已经颇负声名,甚至早在番禾瑞像尚未出世的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番禾瑞像,也称作凉州瑞像,凉州番禾县瑞像或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等不一而足,也有因刘萨诃预言诞生之故而称其为刘萨诃瑞像者,大同小异,皆指今永昌城北圣容寺后依山而立的浮雕瑞像。该像的称名之所以产生了一点小的分歧,主要是对此像的神格、信仰还不能进行准确的区分或界定,而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像是以神格来命名的。番禾瑞像出世的时候,番禾县只是凉州下辖的一个县,凉州则为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属于上下级行政隶属的关系,所以时人在记载此事的时候前面务须要加上“凉州”二字,也就是今之学界大多称其为凉州瑞像的原因。相对来说,在尚未弄清此像系哪一尊佛像的时候,用出世时所在的地名来为其命名是更为合适的,如凉州瑞像、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肥田路美先生称其为凉州番禾县瑞像,将僧传的记载和诞生地都表述出来,无疑更为准确。尚丽新先生简称为番禾瑞像,更加简练,易于表达,笔者在文中也多从此说。另因为此像的出世实是源于刘萨诃之故,也有以刘萨诃之名冠之者,但从后来出土的一些文书、造像及其他相关文物来看,番禾瑞像信仰和刘萨诃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信仰,发展的脉络和传播的地域也互有差别,二者本身表征的意涵也不尽相同。实际上,番禾瑞像应当是释迦牟尼像。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李元封等造的番禾瑞像的题记中就有“释迦圣容立像”之名。若以其神格来为之命名的话,可以称其为“释迦圣容瑞像”,或“释迦圣容立像”,或者叫做“释迦圣容佛”。总之,只要能指明此像即可。
二、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
1.Ⅰ型番禾瑞像
Ⅰ型造像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金川西村出土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造像为砂岩质,残高,8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赤足站立于仰覆莲台上,整个背屏雕成山崖状,背屏右上部已残,颈肩处横贯一道裂纹,头面部及五官残损不清,尚可辨出轮廓。佛像为高浮雕,着衣袒右肩;胸口双领袈裟下边阴刻有锯齿状纹饰;左手握住衣襟一角,左手下部悬出的衣襟层次分明,状若飘起;左边腰部以下至足部的裙襟阳刻有两层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但肘部已不可辨识,应是作与愿印;两腿之间刻有U形纹饰,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排歹。佛像与背屏之间空白处仍残留有浅红色彩,可知原像应当是敷色填彩的。
此像没有任何题记及其它纪年信息,可能是未雕刻或已毁蚀,造成对佛像的时代认定产生了一些分歧。张宝玺先生认为应是北魏所造,文静、魏文斌二位先生认为其造于初唐。业师杜斗城先生在对此像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其制作年代应当在北魏到西魏之间,最迟不会晚于西魏。笔者也认同业师杜斗城先生和张宝玺先生的观点。其残存的头部、身躯以及手臂都比较瘦长;肩部平削,头光和身光连为一体,背光呈上宽下窄的瘦莲瓣形;面部与北魏佛像那种方颐的面庞相类似,整体风格也略显清癯。另从这尊佛像的质地来看,与当地所产石质相同,应当是在本地出产并雕造完成。依此来看,此像应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番禾瑞像的石雕像,这可能对于现存的一些其它造像的时代划分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意义。
2.Ⅱ型番禾瑞像
这尊造像原存于圣容寺大殿东十几米处的一个较大的石窟中,后运至永昌县博物馆保存(图五)。造像为砂岩质,造像通高114厘米,佛像高约94厘米,宽约40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缺,立姿,着衣袒右肩,左手握衣角,胸口双领袈裟下边亦阴刻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肘部以下残损不能辨识;头光是分两层交错雕刻而成,呈莲瓣形;佛像两侧的背光中浮雕有化佛,腰部、肩部和头部两侧对称分布各三身,顶部一身,共七身跏趺坐小化佛。背光呈舟形,再向外则表现出嵯峨的山崖。该石窟现为当地僧俗所雕凿重修,原貌已不存,石窟的情况,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孙修身先生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①原窟室高约2.7米,长宽约3到4米之间,敞口、略称方形;前有长约9米,宽约4.5米,高4米的前廊,与后边的窟室相连。
此像也未留下任何关于纪年的文字信息,孙修身和张宝玺二位先生对其做了简单记录。②张宝玺先生认为此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断代的缘由。③从残存造像所表现出的一些风格特征来看,Ⅱ型的时代要较之于Ⅰ型晚。与Ⅰ型相比,Ⅱ型佛像体型更趋丰满,胸口袈裟的锯齿状纹饰更为明显。头光出现了莲瓣造型,背屏则由瘦莲瓣形变为舟形,并在背屏上浮雕出七身小化佛。
3.Ⅲ型番禾瑞像
Ⅲ型造像被当地人称作“青龙佛”,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永昌县城西南的红山窑乡青龙山庙遗址中被发现,原供奉于青龙山庙之内而得名,后寺庙破毁,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六)。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凿刻而成,部分已残。通高170厘米,宽85厘米,跣足立于仰覆莲台上,体量巨大,与真人几近相等,正是所谓“等身佛”。佛首已断裂,后经修复安装合于一身。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握衣角,下部悬出衣襟;胸口衣领处的锯齿纹及左侧裙边的两层锯齿形纹饰与前面出现的Ⅰ型、Ⅱ型雕刻如出一辙;两腿之间自上而下雕刻有整齐的浅U形纹,膝部以下的衣纹也呈密集的浅U形,衣纹更富韵律感;背屏呈舟形,肩部以上的背屏两侧雕有五身跏趺坐小化佛,顶部已残,顶部可能有一身小佛,两侧对称雕有六身小佛;背屏周边嵯峨的山崖则用浮雕手法表现出来。
佛籍和县志中均没有关于青龙山庙及此像的相关记载,造像本身未雕刻题记,但整尊佛像体量巨大,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衣褶纹饰栩栩如生,表现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法,应是盛唐的作品无疑。
4.番禾瑞像佛首
番禾瑞像佛首于上世纪70年代由原文化馆黄馆长在金川西村望御谷一农户家牛圈墙的垒石中起获,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图七)。佛首为青砂岩质,高67厘米,发髻已残,眉间白毫残缺,鼻、耳朵、唇等处也被磨损。面形圆润,头顶结满低平小螺髻。关于此像的时代和是否为番禾瑞像“原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孙修身、张宝玺二先生对其分别做了记录。孙氏未说明时代,只说其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张氏则认为此像就是佛籍中之凉州瑞像,现存于永昌圣容寺的佛身成于正光元年(520年),而这颗佛首则雕造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佛首的断代还需要进一步判别和认识,因为后世佛首跌落复又安装之次数较多,最初的佛首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基于对相关典籍文献的了解以及对以上儿尊佛像的初步认识,可以通过其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而对永昌出土佛像的时代进行排序。特别是Ⅰ型佛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尊佛像,对于它的出现和进一步认识,可能存在一定的意义: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那尊佛首的认定,而且可能会使以往对身首合璧的番禾瑞像的诞生时代会有新的结论。先来看佛首:孙氏认为佛首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的佛首,实际情况就是在凉州雕刻好佛首之后,又搬运至番禾县望御谷后安装于无头的佛身上;张氏则直接说其雕刻完成于北周元年(557年),是番禾瑞像原像首,根据则不外于道宣的著作。其次,从相关的典籍来看,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身首合璧的那尊体量巨大的“丈八石像”(图八),也就是今天仍然能看到的那尊大的浮雕像。番禾瑞像也应当是在“具足”以后才会被各地“依图供养”其他的小的雕像、造像等等都是依样画葫芦照着原,来的丈八大佛像再行仿制的,这也符合常理。北魏于534年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于557年又为北周所替。但按照文字记载,佛首最早完成与像身的合璧也在北周元年,那么这尊北魏的Ⅰ型佛像怎么会早于北周的丈八石佛出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杜斗城先生很早就指出北魏正光年间望御谷已经出现了造像活动。①在这一系列造像活动中,就可能已经有那种特定造型的佛像被雕造出来,那么这颗佛首就不应该是“原像”了,而是它依照已经成型的番禾瑞像而再行仿制的。如此一来,文献的记载就出现了讹误。第二,正光年间已有佛首刻出,但不知何故丢失,或者说佛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雕刻好,无法安装。北周出现的佛首指的是在凉州东七里涧或其他地方被雕刻出的另外的佛首第三,番禾瑞像是先有像身,后有佛首,其间有“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的分离期。番禾瑞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手印、躯干、衣纹等部位有其自身特点,佛首的形象一般来讲与其他佛像相差不是很大,在近四十余年的空白期是否已经有人先雕出了全像则不得而知,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和典籍中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这就说明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等一系列神异的事件属于附会的可能性极大,信徒为宣扬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对原有的故事“添枝加叶”了。
从以上四尊佛像表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番禾瑞像在当地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造像的细节部分出现了新的装饰,比如增加了莲瓣、化佛以及背屏的变化等等,雕刻更加精美,体量也由小变大。与此同时,望御谷的造像活动自北魏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且不局限于望御谷一地,并在隋唐之际更加兴盛。番禾县当地的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由刘萨诃的神异事迹而衍化出的传说故事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番禾瑞像也为当地僧俗所崇信,使得瑞像信仰在番禾县世代相传。
三、其他代表性造像及文物资料
番禾瑞像“出世”以后,不仅在番禾县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波及到河西走廊及附近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石窟寺遗迹、壁画、雕塑等相关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下选取三个比较典型的出现在河西走廊附近的造像或文物来举例说明。
1.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6窟番禾瑞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开凿于五世纪初,其后历代皆有营修,今仍存70余窟,千佛洞第6窟建于初唐(图九)。该窟坐西向东,高约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佛像高4米。现存于窟内的造像在1992年之前被当地僧俗重修过,与原像的细节特征有出入,特别是原来左手握衣角的造型被改造成了现在的左手托莲台,以致改变了主尊造像的神格,幸得1987年出版的《河西石窟》一书录其原貌。①张善庆先生很早就指出了这次重修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详实的考证。②沙武田先生指出此像“主尊处山形中,时代为唐前期”,③这就说明番禾瑞像背后山崖的表现不是只有将山崖雕饰在佛像背屏上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这种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在地况、材料等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完全可以照搬番禾瑞像最初诞生时的那种方式。张掖东邻永昌,番禾瑞像的造型出现以后,随着瑞像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向西传播的第一站就是张掖,更兼马蹄寺本就是河西之佛教圣地,番禾瑞像在这里的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
2.莫国高窟第72窟南壁番禾瑞像故事画及其他
酒泉、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现存有大量的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相关的遗迹文物,大多是唐、五代及以后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72窟、237窟等。莫高窟72窟南壁的番禾瑞像故事画长约6.5米,高4.3米,下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壁画因流沙磨蚀而不能清晰辨认,西侧下部和东侧也有小部分脱落,仅存上部约三分之一。霍熙亮先生复原了72窟的线描图,并推测其绘于晚唐初期,后经过五代、宋重修。统中国艺术中对宗教偶像最为深刻的思考的画”(图十),①同时也表现了番禾瑞像在身首复合时的情景(图一一),为今天人们了解古代修缮安装佛像的程序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其它如敦煌莫高窟第十六、二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八十四、一二二、三〇〇、三三二等窟,敦煌西千佛洞第十九窟,安西榆林窟第三十三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等石窟均存有番禾瑞像的壁画或塑像,此处不一一详述。
敦煌、酒泉地区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内地的门户,地接西域,又与凉州番禾县相距不远,回鹘、归义军及一些其它短暂出现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大都尊崇佛教,客观上也为瑞像信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数量如此之多的番禾瑞像题材出现于酒泉、敦煌等地,特别是出现于晚唐五代至北宋之际营建的石窟中,就是最好的例证,也足以说明瑞像信仰在这一地区兴盛的程度。
日本滨田德海旧藏的编号为ChinMs:C121的敦煌文书题记中,记录了宋初营修凉州感通寺的一些情况。敦煌研究院马德先生于日本抄录了此文书题记,其内容如下:
文书名: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
正文: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
大祖文皇帝膺千年之圣 百代之英运
属龙非时当凤举廓三籁于道销庇四民于
德寰维释氏之 纲缀儒〔〕之绝纳泽流遐
外九
被无穷 皇帝时乘驭寓幄历君临德
泉道光日月不住无为而孝慈兆庶不 有
为而丘拘万机洞九宅之非絙树三宝之圣福
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靡
又空钟震响寔韵八音灯轮自转 符三点亲
崄者发奇悟于真源传听者荡烦嚣于 派
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
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 栋丹彩于重
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尽人工之妙房
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
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
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
此文本后的题款为“僧道和纪之耳”,故本文皆以“道和文本”称之。这里先简要交代一下“道和文本”所处的唐末五代时期凉州及永昌政治环境变迁的背景①:
唐末五代时期正是河西地区政治势力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相寻的时代凉州先后为吐蕃、归义军、甘州回鹘、嗢末人和凉州吐蕃部等政治势力统治或控制。763年,吐蕃大军开始自东向西攻占唐朝所属的河西地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重兵围攻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未能抵挡吐蕃的猛烈攻势而西奔甘州,河西重镇凉州旋即陷落,766年,吐蕃相继攻下甘州、肃州,河西大部为吐蕃所据,永昌时为凉州所辖,766年之前也已陷于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率部反抗吐蕃,驱逐吐蕃势力,光复了瓜、沙二州。大中三年(849年),张氏自西向东相继收复肃州、甘州。大中五年(851年),唐朝政府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凉州。重镇凉州的攻克,意味着河西走廊基本上已被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在张议潮自西向东进兵的时候,嗢末和一些吐蕃部族也被驱赶到凉州一带,并在这里盘踞下来。中和四年(884年),西迁至河西的回鹘人势力日盛,与甘州原有的吐蕃、退浑等“十五家”部族经常发生战事,这些部族被迫撤出甘州,甘州遂成为回鹘人在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甘州回鹘因此而得名,并在其后逐渐控制了河西地区的大部。十世纪初,以六谷部为首的吐蕃人又入据凉州,取代了原来控制凉州的嗢末等部,成为凉州新的统治者。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以六谷部和折逋家族为首的凉州吐蕃诸部在宋初又臣服于宋。乾德四年(966年),吐蕃部首领折逋支护送欲往天竺取经的六十余名汉僧至甘州,上奏宋庭后,太祖赵匡胤“诏褒答之”①;五年(967年),凉州吐蕃首领闾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等六人向宋朝进贡马匹,可见当时双方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②“道和文本”可能是时间久远或是其他原因,有几处字词不全,从文中透露出的有关圣容寺的信息并不是很丰富,但仍然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以下对此文本做一简单的考释。第一,寺名的问题。文首“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中的“凉州御山感通寺”即今之永昌圣容寺。“天卡来”不明何意,或是讹误之故。孙修身先生认为圣容寺之名是在吐蕃统治凉州时期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第231窟为阴嘉政在吐蕃统治时期所营修,窟内壁画中番禾瑞像旁边的榜题为“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其中有“圣容”一词出现,圣容寺即从此来。实际上,,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资料来看,“圣容”一词早在唐朝就已出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的造像,题记中就有“父母及法界,众生造圣容”等字样。①山西省博物馆藏原存于万荣县的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元封等八人奉造的释迦立像,其台座上铭文刻有“敬造玉石圣容像一区”、“开元廿五年岁次丁丑五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立”等题记①,其中也有圣容一词,说明“圣容”的出现时间是要早于吐蕃的。“道和文本”虽有“圣容”一词,寺名却仍然沿袭了隋唐时期感通寺之名,可见圣容寺之名最早应是出现在北宋乾德年之后了。西夏时期皇陵中供奉帝后神御的寺庙也称为圣容寺,是否和永昌圣容寺互有渊源,尚待进一步详考。②第二,时代和年号。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年),是年十一月癸酉,赵匡胤改元开宝,大赦天下,凉州吐蕃向宋称臣,故沿袭宋之年号。“大祖文皇帝”中“大祖”系“太祖”之误,指宋太祖赵匡胤。“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一句,指的是在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首之后又奉其至感通寺,佛首与像身“宛然符会”之事。“保定”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然此年号只有五年。566年,武帝改元天和,若仍依九年往下推之,则为569年,这就与道宣的记载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道宣《续高僧传》中说:“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依道宣的说法,因瑞像之故,保定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瑞像寺。在修建瑞像寺之初,佛像应当是“灵相圆备”的,如果身首不合就专为其修建寺院,也不合常理,况且北周保定初期,天下太平,也与刘萨诃的预言相符合。那么“道和文本”中这个“保定九年”的记载就是有误的,其记录的内容较《续高僧传》晚出300余年,又不存于史,可见道和的记载也存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是源于当地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过“道和文本”也反映出,从凉州发现佛首义奉至圣容寺安装符会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了,否则不会将其专门记录下来。第三,捐资修寺者。“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栋丹彩于重”两,句中,“汪公”是何许人,无从可考,但身份定然不低,家道亦非常殷实,而且能舍财修寺者必然是虔诚的信佛者,因为塔寺的营修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财的,有了当权者的庇佑和支持,感通寺的香火才会愈加旺盛。第四,营修感通寺的情况。既有身份显贵之人带头舍财以“敬营塔寺”,修建的规模定然不小。文中“塔寺”一词,说明了乾德六年对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也进行了维修。今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始建于唐代,体量巨大,高约12米,其形制与小雁塔极为相似,然最初建塔的情况却于史无考,也未发现有营造碑记,“道和文本”的记录是第一次反映后世营修圣容寺舍利塔的情况。重新营修后的感通寺,“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佛寺的修建总体布局融合了周边的山形地势,修建了大殿、禅室、僧房等等。这次营修不仅修复了过去在兵燹、战乱中受损的塔寺,而且又新修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片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群,几乎是“弥山亘谷,处处僧坊”。其规模之大,甚至可令人“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新修塔寺之壮丽,竟能左望崆峒山,虽不过是形容其盛况的一个借代而已,寺庙规模之盛可见一斑。最后,记录者僧道和。文末题款为“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可知此文是由一名叫道和的僧人所书。道和之名,于僧传、史书皆无可考,这份文书何以能流传至敦煌亦不得而知,然营修感通寺记由道和来笔受,则道和至少应是感通寺中的高僧,甚或就是感通寺的住持。总之,“道和文本”是一份记录北宋初营修感通寺的重要文献,对于考察圣容寺历代的营修和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线边垣达玉关,半渠流水入萧湾。①
红尘不到幽深处,绀宇常浮杏霭间。
佛后洞中仍礼佛,山前寺外更观山。
当年胜地时防虏,花木于今总是闲。
在河西干旱砂碛之地寻得此幽深清静的场所,实属不易,正是佛教弟子出家修行的理想之地。
第一节 刘萨诃的生平及其信仰
圣容寺建寺及番禾瑞像的诞生缘起于刘萨诃西行求法时在凉州番禾县所作的“授记”,因此要了解圣容寺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刘萨诃的生平,特别是刘萨诃在番禾县预言后世将有瑞像出现的史实与传说。
刘萨诃,或称萨荷、萨何、窣(读音“苏”)和、萨河、摩诃等,出家以后法名释慧达,其事迹在正史和佛教典籍中都有收录,相关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如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宝唱的《名僧传》,齐王琰的《冥祥记》,姚思廉《梁书》,南山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下简称为“三宝录”)、《道宣律师感通录》(以下简称为“道宣录”)、《释迦方志》,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以及《永昌县志》等等古籍中都记载了与其相关的事迹。
典籍中多记载刘萨诃为稽胡族,或者叫步落稽。关于这个稽胡族,周一良、唐长孺和林幹等诸位先生有考。实际上,稽胡族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包含了匈奴人后裔、西域胡人以及一些当地土人的“杂胡”,①与匈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一点从刘萨诃的姓氏亦可看出,刘氏、乔氏、呼延氏和郝氏等姓氏为匈奴之大姓,尤以刘氏为多,刘萨诃又出生于世家大族,故其主要的民族成分应当是匈奴族。南北朝时稽胡族主要居住和活动于并州及周围的山区,即今山西西部吕梁、陕北及内蒙南部一带黄土高原的山谷中,以射猎、游牧和简单的农耕生产为业,可能是地理封闭或其他原因所致,其整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程度相对比较落后。唐初的文献中尚能见到零星的有关稽胡族的记载,至中唐以后不见于史书,可能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与刘萨诃相关的文字记载,出现时代最早的应属南朝齐王琰的《冥祥记》,梁慧皎的《高僧传》则出现稍晚。《冥祥记》成书于梁初,王琰则生于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前后,后仕于齐、梁间,虽未出家为僧,但幼年时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而成为佛教弟子,曾游历于交趾、峡表、江都等地,南齐建元元年(479年)之际回到京师。他在书中自称幼年跟从贤法师学习时,得到一尊观世音金像。据其在序言中说,此观音金像能“放光照三尺许,金辉秀起,焕然夺目”;自王琰得到此像以后,“瑞验之发,多自是兴”。从其自述和成书的情况来看,《冥祥记》中未免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不过《冥祥记》成书的时间距后来刘萨诃番禾县望御谷“授记”的时间却是最近的。先来看《冥祥记》,其概要如下: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向西北行。俄见两沙门,谓荷,“汝识我不?”荷答:“不识。”沙门曰:“今宜归命释迦文佛”俄而忽见金色,晖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左右并曰:观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礼。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
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谓荷曰:“汝受轻,罪,又得还生,福力所扶。而今以后,复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遥见故身,意不欲还。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稣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①
《冥祥记》中记载的这一段文字,使得我们可以得知时人对刘萨诃的一些认识:并州西河离石人,即今山西吕梁地区及陕北一带的人。出家为僧之前可能是军卒,喜好田猎,从未听说过有佛法之事。三十一岁时得了暴病却没有死,七日后苏醒。醒来以后就说了一些他在地狱冥游时的经历,诸如受到观世音点化,又因襄阳杀生射鹿而在来世遭受汤镬之刑一类的故事,之后出家,法名释慧达。出家后刘萨诃又去了江东、许昌等地游化,太元末时尚知其在京师,再往后就不知其踪迹了。
王琰关于刘萨诃的记述颇具神话色彩,还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过刘萨诃出家之前和因何出家。首先是确有刘萨诃其人,而且已颇具名气,特别是他暴病之后七日而苏的故事,当时可能流传甚广,否则王琰亦不会在书中列其事迹。刘萨诃出家时已三十一岁,据此可推算其至少生于366年以前,令人费解的是之后这样一位当世名僧就不知所终,杳无音信了,尽管此时正值刘萨诃游化弘法的兴盛期。
梁慧皎的《高僧传》成书较《冥祥记》稍晚,其中也收录了刘萨诃的事迹。《高僧传》所载记事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截止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年),①慧皎本人则卒于梁承圣三年(554年)。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说“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②慧皎乃佛教史家,撰书之立意与方法在此一目了然,又考据详实,删繁补阙,故此书历来为诸家看重。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有关刘萨诃的文字记载,慧皎的记述无疑是相对更为可信的。
《高僧传》卷第十三兴福篇“晋并州竺慧达”载:③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域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313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滬渎口(慧)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尽夜虔礼,未尝暂废。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鄮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蹠。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慧)达东西观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厉,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此处较王琰所记多出了刘萨诃于晋宁康中到京师建康和鄮县等地礼长干寺、拜阿育王塔像等等“屡表征验”的事迹,且刘萨诃暴病而死以后,只用“备见地域苦报”来一笔带过其在地狱冥游时离奇繁复的经历,叙述了一些其在江东吴松、鄮县等地的礼拜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慧皎的这段记述显示出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前后时间跨度很长,至少自西晋建兴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至东晋宁康中时几乎有增无减,其后仍然“东西观礼,终年无改”。在对刘萨诃是否到过河西走廊番禾县并做“授记”一事,尚丽新等先生的观点,①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刘萨诃出现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所历的时间又跨越了三个世纪,而一个人的寿命毫无疑问没有那么长。还需要注意的是,刘萨诃在各地游化时所作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礼忏,甚至“唯以礼忏为先”很明显这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冥祥记》中并未过,多提及刘萨诃礼忏一事,而是更多的描述了其在地狱中遭遇的各种经历,诚然这是刘萨诃在阳世间做了杀生、射猎等种种“恶事”所致,“业力”深重,有因则必有果报。而到了慧皎这里,刘萨诃主要的活动儿乎就是“礼拜悔过,以忏先罪”了。礼拜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即刘萨诃于会稽鄮县(今宁波鄞州区)发现了阿育王塔,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阿育王塔的记载。此后阿育王塔及对刘萨诃本人的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广泛传播,现存的刘萨诃及阿育王塔的文物古迹也存有不少,遍及浙江(图二)①、上海、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图三)②、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另日本也存有不少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是宋代以后的小型金银或铜质塔,源于宋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模仿阿育王营造八万四千塔之事,建造了众多小型阿育王塔,因其多为金铜制作,又叫做金涂塔,此不在本文所述之范围,兹不赘述。但需注意的是,刘萨诃在江左、东南沿海一带,与阿育王塔一起为人们所崇拜,影响很大。刘萨诃礼拜的活动在以后的文献中也多次出现,并且仍然是刘萨诃所作的主要的佛事活动。
其后有关刘萨诃的文字又分别见载于唐初姚思廉的《梁书》和南山律师道宣的几种著作中。《梁书》共五十六卷,实际上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在六世纪中期至七世纪三十年代相继编撰的,历陈、隋、唐三代而成。姚察在陈初曾参与
①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银质阿育王塔及舍利瓶照片。梁史的编修,后又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受命编修,至大业二年(606年)去世时尚未及成书,姚思廉继其父编纂。入唐以后,梁史的监修官正是唐代名臣魏征,姚思廉又受命续修,至其去世前一年(636年)方才成书。故从《梁书》的编修经过来看,有关早期的事迹和记载应当比慧皎的《续高僧传》、《三宝录》和释道世的《法苑珠林》等书要早出。
刘萨诃的事情亦见录于《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载:
有西河离石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①
《梁书》的记载与前述文献的记载总体上大同小异。作为正史,从其用语来看似更加贴合实际,如“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等。刘萨诃礼拜的地域范围却扩大了,出现了洛下、齐城等地。但刘萨诃每到一地,首先要做的且最主要做的仍旧是礼拜,以此来洗脱先前所犯的在佛教看来于理不容的种种罪业。又因为刘萨诃“东西观礼”,礼拜活动的范围很大,而且一直不间断的持续了下去,随着这种礼拜范围的逐步扩大,以及刘萨诃受民间和统治阶层的尊崇,使得这种礼拜活动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甚至有可能成为西北地区民间佛事活动中的一套遵循特定制度的佛教仪轨,或者叫作礼拜法。关于这种礼拜法,现藏于英国图书馆的一个编号为斯4494号的敦煌遗书残卷中,保存了一段名为《刘师礼文》的文献,透露了这种礼拜法的一些有关的形态。斯4494号卷尾的题记是:“(西魏)大统十一年乙丑岁(545)五月廿九日写乞(讫),平南寺道养许”,是南北朝西魏时期平南寺的一位叫道养的僧人个人所持有的写卷,方广錩先生将其定名为“道养文本”,并对这幅残卷做了深入研究。首先判定了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刘师”就是“早期中国信仰性佛教的代表人物——刘萨诃”,其后又讨论了《刘师礼文》中反映出的这个礼拜法的形态。为了达到修持者的目的,即要求修持者于特定的月份特定的日子,在特定的时辰,向某个特定的方向礼拜特定的次数,这样礼拜的效果可以灭除特定的罪孽或者减少罪数,如果能坚持三年,则能成道,所得遂愿;①并在《〈刘师礼文〉中礼拜法初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礼拜法可能被组织成为某种佛教仪轨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礼拜法与早期中国道教的礼忏思想和礼忏形式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和道教相关的情况因囿于笔者所限且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此处不再赘述,但刘萨诃的礼拜活动及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
唐初终南山律师道宣在《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等著述中多次提到刘萨诃的事迹,于其事迹也是著录最丰者。《三宝录》撰成于唐麟德元年(664年),《续高僧传》成书则至迟在麟德二年(665年)。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西晋会稽鄮塔缘一”中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并州离石人刘萨何得病死之后见一梵僧,说其罪重应入地狱,因怜悯他无识而放生,让其往洛下、齐城、丹阳、会稽等地寻浮江石像和阿育王塔并精勤礼拜,死后可免下地狱。醒来后改名慧达,遂出家学佛。后至宁波山中掘得灵塔一座,“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①时人认为这就是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并将涌出塔之山命名为阿育王山至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在刘萨诃礼拜出塔之地又修建了塔亭,这也是阿育王寺建寺之始。鄮县阿育寺又名阿育王广利寺,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宝幢镇,古属会稽郡。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约200年之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将佛祖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每份舍利并造一塔以为供养,在中国共计建有19座舍利塔,这19座塔中因刘萨诃的礼拜活动而建造的塔寺就占了两座,即会稽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干寺塔。
由此可见,刘萨诃是被寄予了厚望的,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能完成好观音交予的种种“任务”,不仅可免自己死后下地狱遭受诸般痛苦惩罚,又能广弘佛法,在自己觉悟成佛的同时引导人们都能觉悟,还能受到人们的尊崇礼敬,岂不是一举多得!自刘萨诃甫一登场,就能感出佛教标志性的建筑物——鄮县阿育王塔和金陵长于寺塔等等,这样的大事之于佛教来说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又因为有死而复生后出家为僧的神奇经历,他在江东各地礼拜佛塔的事迹也逐渐的被增益、神化,原本比较简单的佛事活动又被附会添加了一些灵验的事迹,也使得刘萨诃的生平事迹愈来愈神奇,神话色彩愈加浓厚,直至最后成为了佛教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之一。那么,与此相关的传说自然更多的被附会到刘萨诃的身上,因为自一开始他就是“成大事者”,就有能感通神迹的本领,并且广为人们所熟知,相互传诵,深信不疑,直至最后形成一种信仰。不过此时对刘萨诃的信仰更多的凝结在他个人的身上,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基于对其个人的神奇经历和依附于佛教的感通事迹而言,或可称其为“刘萨诃信仰”。既然他具有能“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在这之后能预言佛像诞生或者其它神异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续高僧传》“感通篇”中记载了刘萨诃的生平:
释慧达,姓刘,名窣(音“苏”)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间,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慧)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①
道宣在此对关于刘萨诃的生平事迹与先前出现的相关记载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其籍贯变成了咸阳东北的三城定阳,而之前大多记载其为西河离石人;其本人“目不识丁,为人凶顽”,家境非常殷实,其后又在襄阳充任一边境小吏。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少、兵痞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不过除了“乐行射猎”以外,没有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他到底干了什么恶事,或者说表达不清,以致于众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低。那么亦有可能道宣在记录此事的时候有意为之,这就使得前后差别显得更大。佛教既要广弘佛法,首先就要证明其“法力”有多么高超,连这种恶少、兵痞一类都能为其所度化,于普通人来讲岂不是更具吸引力。后文又记载:
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慧)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520年)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间,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建德初(572—578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命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575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581—600年)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初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延、丹、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①
道宣虽然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我们还是极需要做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的。同为道宣所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续高僧传》内容也大致相同,此处以《续高僧传》所记的内容为主。通过道宣的记述看出,刘萨诃预言雷震山裂,瑞像现世,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世亦有屡次应验。特别是隋炀帝自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宾客之后,听说了当地这尊佛像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和能预言国之丧乱的功能,专程至瑞相寺礼拜,并亲自书写题名,将“瑞相寺”改名为“感通寺”,让随行的画师图画模写瑞像之形象,分发各地,下令全国的寺院以为供奉。借着最高统治者隋炀帝的尊崇和推广,各地的寺院纷纷供养此像。至此,瑞像的这种独特的信仰由一个地方性的信仰逐渐开始向全国流传,瑞相寺也籍着隋炀帝的布施,由原来规模较小的寺院变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原来不甚知名的、地方性的寺院也日渐声隆,堪称河西名寺,隋炀帝于瑞像信仰的传播及圣容寺的营修建造功不可没。散布在全国各地石窟寺中的番禾瑞像的各种形象,有石雕者,有泥塑者,或图画的,或用绢帛刺绣的①,这些形象也多从炀帝之后雕刻造作。反之,瑞像那种独特的形象通过造像等方式的传播,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传说又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神化了。人们在谈到刘萨诃或是在供奉番禾瑞像时,都能由此而联想到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一系列不平凡的故事经历,二者间“相得益彰”,促使他们各自的信众和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增多增大。
第二节 番禾瑞像
一、番禾瑞像与望御谷
番禾瑞像既诞生于番禾县望御谷,番禾县和望御谷的关系就需要做一简单的了解,尤其是望御谷的情况以前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现在看来,望御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番禾瑞像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番禾一作“番和”,初为汉置县,名番和,魏晋因之,其故治在今永昌县西。望御谷之名最初不知从何而来,亦不见于史册,最初或叫做“御山”。番禾县自西汉置郡以来,一直沿用到晚唐五代宋时期,凡历700多年,期间因为朝代的更替和战争的缘故,有几次暂废和改称,尽管时间都较为短暂,但是番禾郡的故治并未随之而发生变化。从一些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①,番禾古城的规模之大在河西地区也是比较少见的。有说番禾县故址在今焦家庄乡南约一公里处,有说在今之南、北古城一带,皆因没有充足的史料、考古遗迹加以佐证而未有定论,尚待详考,因这一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此处不再展开。但可以确定的是,不论番禾古城的故址在焦家庄乡南或是南北古城一带,其地理方位均在永昌县西,这就与道宣所记载的刘萨诃向东北方向之望御谷“遥礼”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道宣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河西走廊一带。而位于今永昌县城北部的望御谷,也不过就是一个偏僻的峡谷而已,番禾县城就处在望御谷的西南方向,并且中间还隔着武当山,二者相距十几里地,道宣和之前大多数的作者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其记载却丝毫不差。类似于此种夹杂着道听途说式的有关望御谷的记载,说明望御谷在当时就已经颇负声名,甚至早在番禾瑞像尚未出世的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番禾瑞像,也称作凉州瑞像,凉州番禾县瑞像或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等不一而足,也有因刘萨诃预言诞生之故而称其为刘萨诃瑞像者,大同小异,皆指今永昌城北圣容寺后依山而立的浮雕瑞像。该像的称名之所以产生了一点小的分歧,主要是对此像的神格、信仰还不能进行准确的区分或界定,而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像是以神格来命名的。番禾瑞像出世的时候,番禾县只是凉州下辖的一个县,凉州则为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属于上下级行政隶属的关系,所以时人在记载此事的时候前面务须要加上“凉州”二字,也就是今之学界大多称其为凉州瑞像的原因。相对来说,在尚未弄清此像系哪一尊佛像的时候,用出世时所在的地名来为其命名是更为合适的,如凉州瑞像、御容山瑞像、永昌圣容瑞像等。肥田路美先生称其为凉州番禾县瑞像,将僧传的记载和诞生地都表述出来,无疑更为准确。尚丽新先生简称为番禾瑞像,更加简练,易于表达,笔者在文中也多从此说。另因为此像的出世实是源于刘萨诃之故,也有以刘萨诃之名冠之者,但从后来出土的一些文书、造像及其他相关文物来看,番禾瑞像信仰和刘萨诃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信仰,发展的脉络和传播的地域也互有差别,二者本身表征的意涵也不尽相同。实际上,番禾瑞像应当是释迦牟尼像。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李元封等造的番禾瑞像的题记中就有“释迦圣容立像”之名。若以其神格来为之命名的话,可以称其为“释迦圣容瑞像”,或“释迦圣容立像”,或者叫做“释迦圣容佛”。总之,只要能指明此像即可。
二、永昌县当地出土的番禾瑞像
1.Ⅰ型番禾瑞像
Ⅰ型造像于上世纪80年代在金川西村出土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造像为砂岩质,残高,8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赤足站立于仰覆莲台上,整个背屏雕成山崖状,背屏右上部已残,颈肩处横贯一道裂纹,头面部及五官残损不清,尚可辨出轮廓。佛像为高浮雕,着衣袒右肩;胸口双领袈裟下边阴刻有锯齿状纹饰;左手握住衣襟一角,左手下部悬出的衣襟层次分明,状若飘起;左边腰部以下至足部的裙襟阳刻有两层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但肘部已不可辨识,应是作与愿印;两腿之间刻有U形纹饰,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排歹。佛像与背屏之间空白处仍残留有浅红色彩,可知原像应当是敷色填彩的。
此像没有任何题记及其它纪年信息,可能是未雕刻或已毁蚀,造成对佛像的时代认定产生了一些分歧。张宝玺先生认为应是北魏所造,文静、魏文斌二位先生认为其造于初唐。业师杜斗城先生在对此像经过实地考察后,指出其制作年代应当在北魏到西魏之间,最迟不会晚于西魏。笔者也认同业师杜斗城先生和张宝玺先生的观点。其残存的头部、身躯以及手臂都比较瘦长;肩部平削,头光和身光连为一体,背光呈上宽下窄的瘦莲瓣形;面部与北魏佛像那种方颐的面庞相类似,整体风格也略显清癯。另从这尊佛像的质地来看,与当地所产石质相同,应当是在本地出产并雕造完成。依此来看,此像应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番禾瑞像的石雕像,这可能对于现存的一些其它造像的时代划分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意义。
2.Ⅱ型番禾瑞像
这尊造像原存于圣容寺大殿东十几米处的一个较大的石窟中,后运至永昌县博物馆保存(图五)。造像为砂岩质,造像通高114厘米,佛像高约94厘米,宽约40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缺,立姿,着衣袒右肩,左手握衣角,胸口双领袈裟下边亦阴刻锯齿状纹饰,右手下垂,肘部以下残损不能辨识;头光是分两层交错雕刻而成,呈莲瓣形;佛像两侧的背光中浮雕有化佛,腰部、肩部和头部两侧对称分布各三身,顶部一身,共七身跏趺坐小化佛。背光呈舟形,再向外则表现出嵯峨的山崖。该石窟现为当地僧俗所雕凿重修,原貌已不存,石窟的情况,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孙修身先生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①原窟室高约2.7米,长宽约3到4米之间,敞口、略称方形;前有长约9米,宽约4.5米,高4米的前廊,与后边的窟室相连。
此像也未留下任何关于纪年的文字信息,孙修身和张宝玺二位先生对其做了简单记录。②张宝玺先生认为此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断代的缘由。③从残存造像所表现出的一些风格特征来看,Ⅱ型的时代要较之于Ⅰ型晚。与Ⅰ型相比,Ⅱ型佛像体型更趋丰满,胸口袈裟的锯齿状纹饰更为明显。头光出现了莲瓣造型,背屏则由瘦莲瓣形变为舟形,并在背屏上浮雕出七身小化佛。
3.Ⅲ型番禾瑞像
Ⅲ型造像被当地人称作“青龙佛”,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永昌县城西南的红山窑乡青龙山庙遗址中被发现,原供奉于青龙山庙之内而得名,后寺庙破毁,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六)。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凿刻而成,部分已残。通高170厘米,宽85厘米,跣足立于仰覆莲台上,体量巨大,与真人几近相等,正是所谓“等身佛”。佛首已断裂,后经修复安装合于一身。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握衣角,下部悬出衣襟;胸口衣领处的锯齿纹及左侧裙边的两层锯齿形纹饰与前面出现的Ⅰ型、Ⅱ型雕刻如出一辙;两腿之间自上而下雕刻有整齐的浅U形纹,膝部以下的衣纹也呈密集的浅U形,衣纹更富韵律感;背屏呈舟形,肩部以上的背屏两侧雕有五身跏趺坐小化佛,顶部已残,顶部可能有一身小佛,两侧对称雕有六身小佛;背屏周边嵯峨的山崖则用浮雕手法表现出来。
佛籍和县志中均没有关于青龙山庙及此像的相关记载,造像本身未雕刻题记,但整尊佛像体量巨大,丰满圆润,线条流畅,衣褶纹饰栩栩如生,表现出娴熟高超的雕刻技法,应是盛唐的作品无疑。
4.番禾瑞像佛首
番禾瑞像佛首于上世纪70年代由原文化馆黄馆长在金川西村望御谷一农户家牛圈墙的垒石中起获,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图七)。佛首为青砂岩质,高67厘米,发髻已残,眉间白毫残缺,鼻、耳朵、唇等处也被磨损。面形圆润,头顶结满低平小螺髻。关于此像的时代和是否为番禾瑞像“原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孙修身、张宝玺二先生对其分别做了记录。孙氏未说明时代,只说其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张氏则认为此像就是佛籍中之凉州瑞像,现存于永昌圣容寺的佛身成于正光元年(520年),而这颗佛首则雕造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佛首的断代还需要进一步判别和认识,因为后世佛首跌落复又安装之次数较多,最初的佛首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对永昌出土造像的一些认识
基于对相关典籍文献的了解以及对以上儿尊佛像的初步认识,可以通过其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而对永昌出土佛像的时代进行排序。特别是Ⅰ型佛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尊佛像,对于它的出现和进一步认识,可能存在一定的意义: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那尊佛首的认定,而且可能会使以往对身首合璧的番禾瑞像的诞生时代会有新的结论。先来看佛首:孙氏认为佛首就是《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的佛首,实际情况就是在凉州雕刻好佛首之后,又搬运至番禾县望御谷后安装于无头的佛身上;张氏则直接说其雕刻完成于北周元年(557年),是番禾瑞像原像首,根据则不外于道宣的著作。其次,从相关的典籍来看,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身首合璧的那尊体量巨大的“丈八石像”(图八),也就是今天仍然能看到的那尊大的浮雕像。番禾瑞像也应当是在“具足”以后才会被各地“依图供养”其他的小的雕像、造像等等都是依样画葫芦照着原,来的丈八大佛像再行仿制的,这也符合常理。北魏于534年之后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于557年又为北周所替。但按照文字记载,佛首最早完成与像身的合璧也在北周元年,那么这尊北魏的Ⅰ型佛像怎么会早于北周的丈八石佛出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杜斗城先生很早就指出北魏正光年间望御谷已经出现了造像活动。①在这一系列造像活动中,就可能已经有那种特定造型的佛像被雕造出来,那么这颗佛首就不应该是“原像”了,而是它依照已经成型的番禾瑞像而再行仿制的。如此一来,文献的记载就出现了讹误。第二,正光年间已有佛首刻出,但不知何故丢失,或者说佛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雕刻好,无法安装。北周出现的佛首指的是在凉州东七里涧或其他地方被雕刻出的另外的佛首第三,番禾瑞像是先有像身,后有佛首,其间有“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的分离期。番禾瑞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手印、躯干、衣纹等部位有其自身特点,佛首的形象一般来讲与其他佛像相差不是很大,在近四十余年的空白期是否已经有人先雕出了全像则不得而知,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和典籍中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这就说明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等一系列神异的事件属于附会的可能性极大,信徒为宣扬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而对原有的故事“添枝加叶”了。
从以上四尊佛像表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番禾瑞像在当地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造像的细节部分出现了新的装饰,比如增加了莲瓣、化佛以及背屏的变化等等,雕刻更加精美,体量也由小变大。与此同时,望御谷的造像活动自北魏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且不局限于望御谷一地,并在隋唐之际更加兴盛。番禾县当地的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由刘萨诃的神异事迹而衍化出的传说故事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番禾瑞像也为当地僧俗所崇信,使得瑞像信仰在番禾县世代相传。
三、其他代表性造像及文物资料
番禾瑞像“出世”以后,不仅在番禾县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波及到河西走廊及附近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石窟寺遗迹、壁画、雕塑等相关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下选取三个比较典型的出现在河西走廊附近的造像或文物来举例说明。
1.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6窟番禾瑞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开凿于五世纪初,其后历代皆有营修,今仍存70余窟,千佛洞第6窟建于初唐(图九)。该窟坐西向东,高约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佛像高4米。现存于窟内的造像在1992年之前被当地僧俗重修过,与原像的细节特征有出入,特别是原来左手握衣角的造型被改造成了现在的左手托莲台,以致改变了主尊造像的神格,幸得1987年出版的《河西石窟》一书录其原貌。①张善庆先生很早就指出了这次重修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详实的考证。②沙武田先生指出此像“主尊处山形中,时代为唐前期”,③这就说明番禾瑞像背后山崖的表现不是只有将山崖雕饰在佛像背屏上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这种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在地况、材料等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完全可以照搬番禾瑞像最初诞生时的那种方式。张掖东邻永昌,番禾瑞像的造型出现以后,随着瑞像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向西传播的第一站就是张掖,更兼马蹄寺本就是河西之佛教圣地,番禾瑞像在这里的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
2.莫国高窟第72窟南壁番禾瑞像故事画及其他
酒泉、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现存有大量的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相关的遗迹文物,大多是唐、五代及以后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72窟、237窟等。莫高窟72窟南壁的番禾瑞像故事画长约6.5米,高4.3米,下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壁画因流沙磨蚀而不能清晰辨认,西侧下部和东侧也有小部分脱落,仅存上部约三分之一。霍熙亮先生复原了72窟的线描图,并推测其绘于晚唐初期,后经过五代、宋重修。统中国艺术中对宗教偶像最为深刻的思考的画”(图十),①同时也表现了番禾瑞像在身首复合时的情景(图一一),为今天人们了解古代修缮安装佛像的程序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其它如敦煌莫高窟第十六、二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八十四、一二二、三〇〇、三三二等窟,敦煌西千佛洞第十九窟,安西榆林窟第三十三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等石窟均存有番禾瑞像的壁画或塑像,此处不一一详述。
敦煌、酒泉地区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内地的门户,地接西域,又与凉州番禾县相距不远,回鹘、归义军及一些其它短暂出现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大都尊崇佛教,客观上也为瑞像信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数量如此之多的番禾瑞像题材出现于酒泉、敦煌等地,特别是出现于晚唐五代至北宋之际营建的石窟中,就是最好的例证,也足以说明瑞像信仰在这一地区兴盛的程度。
日本滨田德海旧藏的编号为ChinMs:C121的敦煌文书题记中,记录了宋初营修凉州感通寺的一些情况。敦煌研究院马德先生于日本抄录了此文书题记,其内容如下:
文书名: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
正文: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
大祖文皇帝膺千年之圣 百代之英运
属龙非时当凤举廓三籁于道销庇四民于
德寰维释氏之 纲缀儒〔〕之绝纳泽流遐
外九
被无穷 皇帝时乘驭寓幄历君临德
泉道光日月不住无为而孝慈兆庶不 有
为而丘拘万机洞九宅之非絙树三宝之圣福
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靡
又空钟震响寔韵八音灯轮自转 符三点亲
崄者发奇悟于真源传听者荡烦嚣于 派
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
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 栋丹彩于重
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尽人工之妙房
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
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
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
此文本后的题款为“僧道和纪之耳”,故本文皆以“道和文本”称之。这里先简要交代一下“道和文本”所处的唐末五代时期凉州及永昌政治环境变迁的背景①:
唐末五代时期正是河西地区政治势力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相寻的时代凉州先后为吐蕃、归义军、甘州回鹘、嗢末人和凉州吐蕃部等政治势力统治或控制。763年,吐蕃大军开始自东向西攻占唐朝所属的河西地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重兵围攻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未能抵挡吐蕃的猛烈攻势而西奔甘州,河西重镇凉州旋即陷落,766年,吐蕃相继攻下甘州、肃州,河西大部为吐蕃所据,永昌时为凉州所辖,766年之前也已陷于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率部反抗吐蕃,驱逐吐蕃势力,光复了瓜、沙二州。大中三年(849年),张氏自西向东相继收复肃州、甘州。大中五年(851年),唐朝政府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凉州。重镇凉州的攻克,意味着河西走廊基本上已被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在张议潮自西向东进兵的时候,嗢末和一些吐蕃部族也被驱赶到凉州一带,并在这里盘踞下来。中和四年(884年),西迁至河西的回鹘人势力日盛,与甘州原有的吐蕃、退浑等“十五家”部族经常发生战事,这些部族被迫撤出甘州,甘州遂成为回鹘人在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甘州回鹘因此而得名,并在其后逐渐控制了河西地区的大部。十世纪初,以六谷部为首的吐蕃人又入据凉州,取代了原来控制凉州的嗢末等部,成为凉州新的统治者。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以六谷部和折逋家族为首的凉州吐蕃诸部在宋初又臣服于宋。乾德四年(966年),吐蕃部首领折逋支护送欲往天竺取经的六十余名汉僧至甘州,上奏宋庭后,太祖赵匡胤“诏褒答之”①;五年(967年),凉州吐蕃首领闾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等六人向宋朝进贡马匹,可见当时双方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②“道和文本”可能是时间久远或是其他原因,有几处字词不全,从文中透露出的有关圣容寺的信息并不是很丰富,但仍然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以下对此文本做一简单的考释。第一,寺名的问题。文首“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中的“凉州御山感通寺”即今之永昌圣容寺。“天卡来”不明何意,或是讹误之故。孙修身先生认为圣容寺之名是在吐蕃统治凉州时期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第231窟为阴嘉政在吐蕃统治时期所营修,窟内壁画中番禾瑞像旁边的榜题为“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其中有“圣容”一词出现,圣容寺即从此来。实际上,,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资料来看,“圣容”一词早在唐朝就已出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的造像,题记中就有“父母及法界,众生造圣容”等字样。①山西省博物馆藏原存于万荣县的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元封等八人奉造的释迦立像,其台座上铭文刻有“敬造玉石圣容像一区”、“开元廿五年岁次丁丑五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立”等题记①,其中也有圣容一词,说明“圣容”的出现时间是要早于吐蕃的。“道和文本”虽有“圣容”一词,寺名却仍然沿袭了隋唐时期感通寺之名,可见圣容寺之名最早应是出现在北宋乾德年之后了。西夏时期皇陵中供奉帝后神御的寺庙也称为圣容寺,是否和永昌圣容寺互有渊源,尚待进一步详考。②第二,时代和年号。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年),是年十一月癸酉,赵匡胤改元开宝,大赦天下,凉州吐蕃向宋称臣,故沿袭宋之年号。“大祖文皇帝”中“大祖”系“太祖”之误,指宋太祖赵匡胤。“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一句,指的是在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首之后又奉其至感通寺,佛首与像身“宛然符会”之事。“保定”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然此年号只有五年。566年,武帝改元天和,若仍依九年往下推之,则为569年,这就与道宣的记载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道宣《续高僧传》中说:“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依道宣的说法,因瑞像之故,保定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瑞像寺。在修建瑞像寺之初,佛像应当是“灵相圆备”的,如果身首不合就专为其修建寺院,也不合常理,况且北周保定初期,天下太平,也与刘萨诃的预言相符合。那么“道和文本”中这个“保定九年”的记载就是有误的,其记录的内容较《续高僧传》晚出300余年,又不存于史,可见道和的记载也存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是源于当地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过“道和文本”也反映出,从凉州发现佛首义奉至圣容寺安装符会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了,否则不会将其专门记录下来。第三,捐资修寺者。“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栋丹彩于重”两,句中,“汪公”是何许人,无从可考,但身份定然不低,家道亦非常殷实,而且能舍财修寺者必然是虔诚的信佛者,因为塔寺的营修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财的,有了当权者的庇佑和支持,感通寺的香火才会愈加旺盛。第四,营修感通寺的情况。既有身份显贵之人带头舍财以“敬营塔寺”,修建的规模定然不小。文中“塔寺”一词,说明了乾德六年对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也进行了维修。今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始建于唐代,体量巨大,高约12米,其形制与小雁塔极为相似,然最初建塔的情况却于史无考,也未发现有营造碑记,“道和文本”的记录是第一次反映后世营修圣容寺舍利塔的情况。重新营修后的感通寺,“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佛寺的修建总体布局融合了周边的山形地势,修建了大殿、禅室、僧房等等。这次营修不仅修复了过去在兵燹、战乱中受损的塔寺,而且又新修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片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群,几乎是“弥山亘谷,处处僧坊”。其规模之大,甚至可令人“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新修塔寺之壮丽,竟能左望崆峒山,虽不过是形容其盛况的一个借代而已,寺庙规模之盛可见一斑。最后,记录者僧道和。文末题款为“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可知此文是由一名叫道和的僧人所书。道和之名,于僧传、史书皆无可考,这份文书何以能流传至敦煌亦不得而知,然营修感通寺记由道和来笔受,则道和至少应是感通寺中的高僧,甚或就是感通寺的住持。总之,“道和文本”是一份记录北宋初营修感通寺的重要文献,对于考察圣容寺历代的营修和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附注
①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148-156页。
①亦有人称“小湾”者,系误称,即此南济汉《后大寺》诗中之“萧湾”,系同音异字,指同一处地方,即今金川峡水库西侧靠近长城一带。准确的称呼当是“萧湾”,因当地萧姓族人而名,嘉庆二十一年本《永昌县志·水利图》标记其为“萧家湾”。
①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148-156页
①法苑珠林》卷八十六引《冥祥记》。
①[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4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①尚丽新:《“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76-82页。
①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银质阿育王塔及舍利瓶照片。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2009年第2期,39页。
②福建泉州开元寺东塔塔基浮雕拓片,右侧四字为“萨诃朝塔”。描绘刘萨诃礼拜阿育王塔,塔从地涌出之故事。
①[唐]姚思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1—792页
①方广錩:《试论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汇流——从〈刘师
礼文〉谈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37—42页。
②方广錩:《〈刘师礼文〉中礼拜法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27页。
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
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
①[日]肥田路美著,牛源译:《凉州番禾县瑞像故事及造型》,《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165—180页
①参考清代诸版本《永昌县志》。
①孙修身:《古凉州番禾县调查记》,《西北民族文丛》第三辑,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研究所,1983年,147—154页。
②孙修身在《古凉州番禾县调查记》中未说明此像的具体时代,只记录其“当为早期的造像”;《甘肃佛教石刻造像》“永昌圣容寺造像碑”条下记其为“北魏,砂岩……,背光上布七身小佛”,未作更详细记录。
③同上。
①杜斗城:《刘萨诃与凉州番禾望御山“瑞像”》,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年,第164页。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141。
②张善庆:《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千佛洞凉州瑞像再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80—84页。
③沙武田:《敦煌石窟历史的重构—敦煌吐蕃期洞窟诸现象之省思》,《圆光佛学学报(11卷)》,2007年62页。
①这幅壁画也是番禾瑞像整个出世过程最为完整的一个表现,巫鸿先生称其是“一幅极其复杂的、可能是传
①霍熙亮:《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瑞像史迹变》,《文物》,1993年第2期,32—47页。
①[美]巫鸿:《再论刘萨诃》,《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431—454页。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153页。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153页。
②同上。
①文静,魏文斌:《唐代石雕刘萨诃瑞像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2期。
①文静,魏文斌:《唐代石雕刘萨诃瑞像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2期。
②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100—102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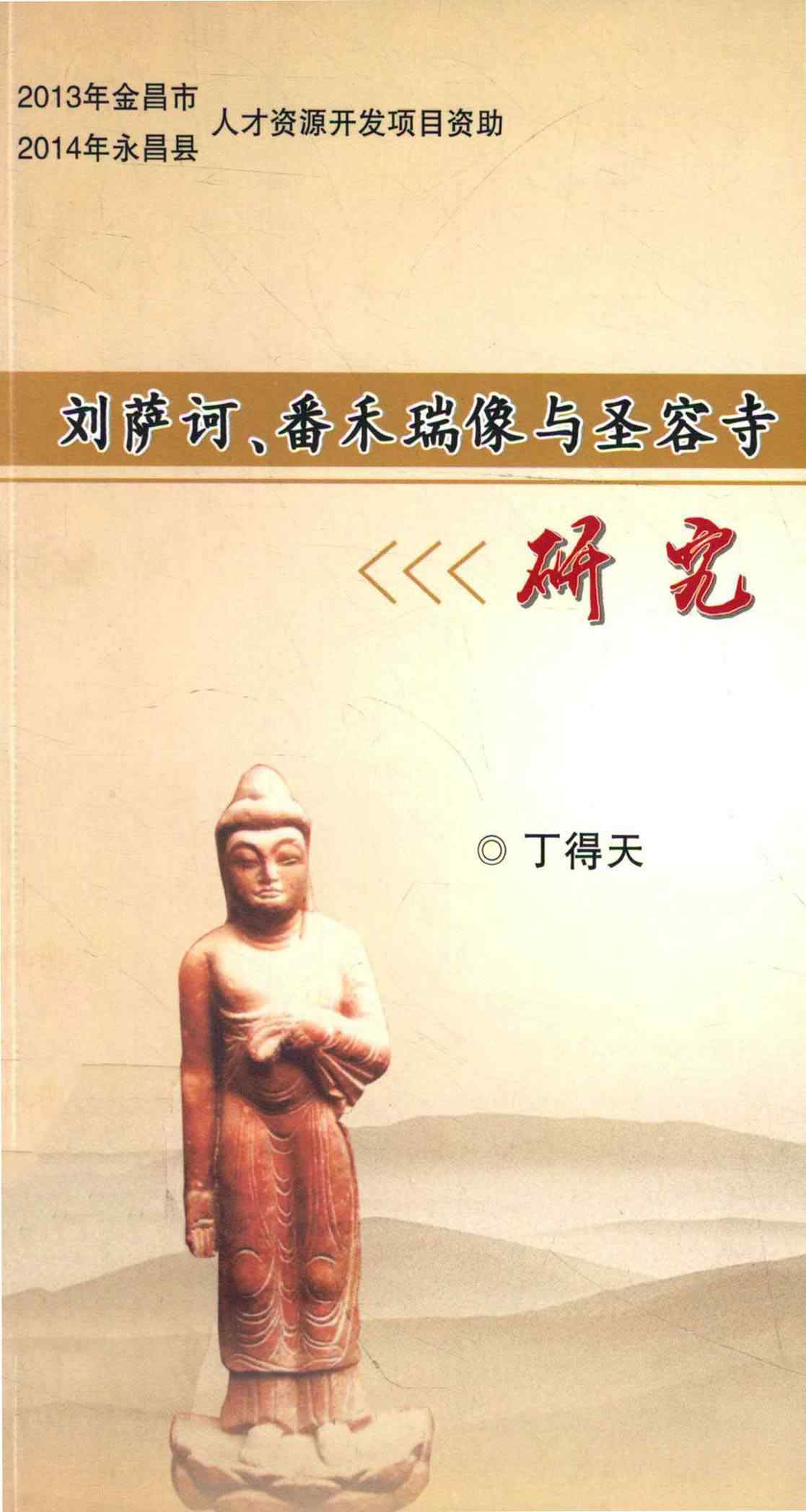
《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介绍了刘萨诃的生平以及番禾瑞像和圣容寺的情况,对望御谷及周边的佛教遗迹做了全面的调查,著录了金昌市境内散见的佛教石窟寺遗迹以及清代《永昌县志》所记载的古寺。
阅读
相关地名
永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