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以基督教约翰王传说为例
| 内容出处: |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39 |
| 颗粒名称: | 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以基督教约翰王传说为例 |
| 分类号: | K203-5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97-106 |
| 摘要: | 本文从以基督教约翰王传说为例论证了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过程,约翰王的传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
| 关键词: | 基督教 文化研究 历史研究 |
内容
约翰王(PresterJohn)是一个12至17世纪期间欧洲教会和诸侯所熟知的名字。他的传说因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的一封署有这个名字的信件而在欧洲风行。该信称约翰王统治的地区物产丰饶、子民和谐,并承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基督教对付敌人。该信件自问世后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先后出现了德、法、英、拉丁等语言的100多个抄本。约翰王及其传说影响深远,甚至在哥伦布以后多年仍能唤起欧洲人的热情。当然,约翰王的传说确有些荒诞不经,但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去考察,便可发现,它反映了中世纪西方人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对美好社会追求的内在价值。一、约翰王及其信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亚洲在欧洲人的印象中只是一张充斥着想象和传说的地图。有关约翰王的传说便是其中之一。最初,欧洲的朝圣者和旅行者把名字及其故事传人欧洲:在遥远的中亚,有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其统治者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长老——约翰·普里斯特,是《圣经》拜见圣婴耶稣的东方三博士的后裔。他在中亚所向披靡,声名显赫,俨然拥有着一座域外的上帝之城。1145年,德国主教奥托在其著作中提到,一位叙利亚主教亲口向他讲述了这位基督教约翰王的故事,说他打算到耶路撒冷与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并肩作战。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署名“约翰王”的信。信中介绍了约翰王的显赫地位、财富及其对基督教的虔诚,引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兴趣。这封信迅速被译成12种以上的欧洲文字,人们争相传抄和阅读。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约翰回了一封,并派遣了曾到过东方的医师菲利普(Philip)作为信使。①
当时,欧洲的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家对约翰王及其王国纷纷进行猜测。一部分人认为约翰王在印度,这可能是把他与传教士圣·托马斯混淆了。另一些人认为约翰王国应位于中亚某个未知地区的中心。上述猜测的依据是这两块地区分布有涅斯托里教派和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组织。不过,到14世纪,大部分欧洲学者已放弃了该王国在亚洲的猜想,而认为它在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王国。到16世纪末时,约翰王出现在荷兰人和德国人绘制的南部或东部非洲地图上。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德国学者为首的国际学术界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迄今不衰。概而言之,关于约翰王及其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约翰王人物原型的研究。约翰王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马可·波罗认为,蒙古草原部落克烈部首领王罕脱里才是真正的约翰王。1322—1328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岛中国旅行,把汪古部的首领当作了约翰王,并指出以往关于约翰王的种种传说不足为信。①研究该问题的先驱学者古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和弗雷德里希·赞克(FriedrichZarncke)认为,约翰王就是中亚Qara-Khitay帝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②鲁布鲁克认为,约翰王是指乃蛮部的屈出律。俄国学者布鲁恩(Ph.Bruun)于1976年提出,约翰王应在格鲁吉亚中寻找,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格鲁吉亚正在经历对穆斯林势力形成挑战的军事复兴。③M.巴伊兰(M.Bar-Ilan)则认为,约翰王信中的约翰居住在印度,而不是埃塞俄比亚。④1923年,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马里涅斯库(ConstantineMarinescu)认为约翰王的原型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1931年,意大利学者李奥纳多·奥勒斯吉(LeonardoOlschki)另辟蹊径,首先提出约翰王传说只是乌托邦。他相信,约翰王及其信件并没有历史原型,根据地理寻找他的王国毫无用处。此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如有人认为这个传说是混合了某些放纵诗人与朋友取乐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当代研究者已经放弃了固执一说的做法,而更注重对该传说历史演变的考察,例如大卫·摩尔根(DavidMorgan)考察了13世纪期间约翰王“候选人”的变化过程。⑤
第二,关于约翰王传说缘起的研究。关于该传说产生的根源,学术界的观点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寻找基督教盟友。约翰·拉纳(JohnLarner)认为,约翰王的传说表达了西方人寻找对付穆斯林的天然联盟的一种强烈愿望。①中国学者吴莉苇也认为,十字军东征时期凡有远东的军队攻打穆斯林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涉及的地理区域都被编入约翰王的故事中,那些穆斯林的敌人们就被基督徒设想为约翰王及其臣民。②瓦西里耶夫(A.A.Vasiliev)也指出,约翰王的信件于14或15世纪在俄罗斯流行也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盟友,以消除鞑靼人的威胁。③ 第二,欧洲神权与世俗权力之争的需要。例如,汉密尔顿认为,该信件是德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Barbarossa)差人伪造的,是他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斗争期间宣传的组成部分。④
第三,借以改善欧洲基督教社会道德状况。李奥纳多·奥勒斯吉认为,欧洲人虚构约翰王的目的是表达对当时欧洲基督教分裂状况的讽刺,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其目的在于改善欧洲人已经败坏的社会道德。⑤ 第三,该信件作者身份的研究。由于该信件出现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人认为约翰王“部分上是十字军想象世界的一个产物”,即此信作者应为基督教会的教士。李奥纳多·奥勒斯吉也认为其作者是西方教会的一个牧师,但他在信中只是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M.巴伊兰认为约翰王之信的作者是中世纪意大利的犹太人。⑥伯纳德·汉米尔顿(BernardHamilton)将其视为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为政治目的伪造品,可能由费雷德里克国王的大法官,科隆的大主教莱纳德·冯·达赛尔(Rainaldvon Dassel)炮制而成。⑦国内的龚缨晏先生运用中国古籍与国外学者长期研究成果相对照,对各种观点给予了评述,但并未表示支持其中的一种。⑧
二、中世纪西方对约翰王的“寻觅”
(一)雾里看花:11~12世纪,印度神奇的约翰王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西方的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为了巩固和扩大天主教的势力,极力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地中海东岸国家和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企图建立“世界教会”。然而,阿拉伯国家此时势力已经壮大起来,并对西方世界构成强大的威胁。尤其是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SeljuqTurks)占领了耶路撒冷,对教皇和基督教世界打击很大。欧洲人渴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但是多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成果,加之罗马教皇与欧洲各君主争权夺利,使整个欧洲社会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
于是,他们开始寄希望于在穆斯林世界的东面能有同盟者,约翰王的故事也就不胫而走。约翰王的原型可追溯到《新约》中的“约翰王”的提法。①在传入欧洲之前,约翰王的故事也许在亚洲的聂思脱里教派中流传已久。1122年,一名自称来自印度主教约翰(PatriarchJohn)到达罗马,要求教皇承认他的职位。这名主教约翰声称,自己所在的胡尔南(Hulna)城建在婆黑森(Phison)河边,规模和势力很大,虔诚的基督徒居住其中。城市外,十二僧侣为了纪念十二圣徒修建了圣托马斯大教堂,在他的斋戒日全亚洲的基督徒都来参观。②对此,约翰·拉纳表示:“我们面对的不过是某个自信的骗子,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制造出把戏糊弄教皇。”③ 但是,这个在东方影响力很大的基督教团体的故事还是被传播开来。
最早一份关于约翰王的记载见于德国弗赖辛(Freising)的奥托主教(BishopOtto)1145年发表的《编年史》。奥托声称亲自见到来自安条克公国的主教休(BishopHugh)向罗马教皇尤金三世(PopeEugeniusⅢ)报告说,在世界的最东方,有一名国王兼长老的约翰,是基督教徒,是《圣经》中的古代东方三博士④的直系后裔,曾打败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穆斯林国王塞米阿第(Samiardi)兄弟,并攻占了其都城埃克巴塔那(Ekbatana)。他受到祖先的激励,想到圣城耶路撒冷朝拜,但因军队无法穿越底格里斯河而退兵。根据学者的研究,休提到的这场战役可能是1141年哈喇契丹(1124—1211年,即西辽帝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Yeh-lüTa-shih,1094—1143年)与塞尔柱苏丹桑贾尔(SultanSanjar)在中亚河中地区卡特万(Oatwan)的会战,结果后者战败导致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这块地区。而耶律大石的突厥语称号“葛儿罕”(汉字又译作“古儿汗”、“菊儿罕”等),读音后讹传为希伯来文的Yohanan或叙利亚文的Yuhanan,由此再转化为拉丁文的Johannes或John。①经学者考证,耶律大石本人并非佛教徒,而是萨满教或后改信佛教徒,因而休提到的约翰王误以为是耶律大石②,但耶律大石统治部落中确有涅斯托教徒。
在1165年,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没有地址的“约翰王之信”。这位约翰王首先声明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城中的基督教徒处处受到保护”,但也有不少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民。其次自己的王国疆域广大,“统治三个印度”,“如果您确想知道我的权限范围的话,那么请您坚信,我,约翰·普里斯特的统治至高无上,其美德超群,我十分富有,统治着天下的万物生灵。” “地上蜂蜜流淌,处处都有牛奶”,“到处有着奇珍异宝”。皇宫金碧辉煌,“采用圣托马斯为King Gundoforus设计的模式建成”,经常用隆重盛大的宴会款待子民。“在这里没有做伪证者、货币伪造者、私通者或强奸者”。最后,讲述国内神奇事物。城内有亚历山大之门(theGateofAlexander)和不老泉,有一个魔镜能够看到自己统治区域的任何角落。
由此来看,约翰王及其传说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是欧洲人在没有使者或传教士亲自到亚洲考察前对东方的想象,其中的“错误”自然难免,例如信中所谓的“三个印度”③,以“近印度”向东最为突出。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印度就是世界的最东方,约翰王就是东方的统治者。这种想象很可能是根据亚洲的聂思脱里教徒或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道听途说的亚洲战事,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军事的失利需要外部帮助的需求下产生并广泛传播的。
(二)犹抱琵琶:13~14世纪,中亚草原上的约翰王
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大军的西征使东西方的碰撞与认知成为可能。随着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顺利进行,基督教徒占领了兄弟国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暴露了罗马教皇积极寻求对已知世界的封建君主的权位争夺,而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在黑海和其他东方地区“发现”了更多的基督教徒,并错误地认为穆斯林世界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超过了穆罕默德的信仰者。这无疑激发了罗马教皇更大的野心,也更加使欧洲人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位皈依基督教的约翰王将会帮助他们取得尘世和精神的巨大胜利。
13世纪初,蒙古人的迅速崛起与对外扩张是西方人始料未及的。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三次西征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对于这个彪悍、野蛮的可怕民族,西方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并企图到他们中去寻找梦寐以求的约翰王。
1221年,随十字军东征至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巴勒斯坦的阿克雷主教(BishopofAcre)德维特里(JacquesdeVitry)和西部教会的佩拉吉斯枢机(Cardinal Pelagius)向罗马报告说:“两个印度的国王”大卫王正率领着彪悍的军队帮助基督教武士们,并吞掉了强大的撒拉逊国。他是约翰王的儿子或孙子。①其实,他们所指的大卫王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因为后者在1219—1222年间攻灭了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花刺子模(Kharezm),并占领了波斯东部的呼罗珊诸地。这让欧洲的基督教徒们群情激昂,更加坚信约翰王的存在,并将之视为攻打穆斯林的天然同盟。
1240年前后,蒙古人的铁蹄踏进欧洲,使欧洲人关于约翰王的美梦变成了歌各和玛各的噩梦。其实,最早意识到蒙古人威胁的是穆斯林异端亦思马因人。他们在1238年曾向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建议结成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大同盟共同对付来自东方的可怕敌人。但是,这一建议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当时西欧教俗权力之争,尤其德皇腓特烈一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根本无暇顾及尚未成为重大威胁的蒙古人;同时蒙古人对穆斯林世界的打击,让欧洲人乐于坐山观虎斗,想渔翁得利,让“全球变得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基督”。
拔都第二次西征,饮马多瑙河,里格尼茨打败西波联军。这使西方世界惊慌失措,各种猜测随之产生。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Paris)满怀恐惧与憎恨地称,蒙古人就是《圣经》中预言的来摧毁基督子民的歌各和玛各的后代,他们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 。他认为,这也许是上帝假鞑靼人之手来惩罚他们的罪过。
与此同时,教皇格里九世呼吁组织十字军抵御蒙古人。但是,由于德皇与罗马教徒互相攻讦而流产。③1245年,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集中讨论如何防止蒙古侵略的问题。一面对防御工作,一面派遣教士充当使者,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戮基督教和侵犯欧洲,并企图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随后,罗马教会和国王纷纷派遣传教士前往寻求约翰王。其中有著名的博朗·嘉宾、阿西林使团、路布鲁克等人出使蒙古,尽管结盟的使命没有完成,但他们得知蒙古人中有不少聂斯托里教徒,使得欧洲人依然坚信在鞑靼人和穆斯林所构成的屏障以外存在约翰王的国度。
在此期间,1241年窝阔台大汗病逝,致使在欧洲征服的王子们抽兵回国,西征暂时停止。此后,蒙古人再也没有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攻势。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噩梦。于是,他们编造出各种说法来描述他们是如何打败和赶走了蒙古人。1253年,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摧毁巴格达和叙利亚,让基督教世界一片喝彩。蒙古人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认为蒙古人是伊斯兰教的天敌,是上帝的意志让穆斯林招致灭顶之灾。但是,蒙古人对待欧洲的反复无常,让他们相信,蒙古人肯定不是他们所期盼的约翰王。
在此背景下,马可·波罗的叙述充当了确认歌各和玛各之地与约翰王之国地理位置的重要角色。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从六十三章至六十七章、七十二至七十三章节中都涉及约翰王的问题。①其大体内容如下:1.鞑靼人确实是居住在北方的玛各人②。但歌各与玛各之地曾被约翰王③所征服,但现在约翰王的国土又被鞑靼人征服。2.可汗宽容那些不反对帝国臣民的各种信仰,因基督教徒战前占卜成吉思汗取胜,故优待基督教徒。3.鞑靼人与约翰王之后联姻,如成吉思汗纳王罕之女为妾,四子拖雷娶一女。而约翰国王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公主为妻。
尽管马可·波罗在该问题认识上出现了不少史实性错误,但他为鞑靼人和约翰王这原本敌对的两族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约翰王也不再是传奇中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被蒙古人打败的真实人物。最关键的是,马可·波罗认为,契丹是鞑靼人统治的约翰王之旧地,并仍有众多基督教徒生活其中。④而且,在契丹南面是居民为偶像教徒的蛮子国。⑤这使得欧洲人对“大印度”之中的“近印度”多了一些具体的知识。但在蒙古帝国瓦解后,欧洲人开始动摇这个念头:约翰王是否确实是中亚大草原上的某个国王。⑥随着13世纪末天主教派来到元朝,聂斯托里派在大草原上的历史逐渐结束,约翰王及其传说也随之淡出亚洲。
(三)蓦然回首:14~18世纪非洲的约翰王国
蒙古作为一个霸权国在亚洲的兴起以及商业在欧亚世界体系中的扩展,西方人开始意识到最遥远的亚洲内地与约翰王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是,欧洲人很快为他在未知的和神秘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个新家。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除了欧洲人对亚洲约翰王的幻想破灭外,埃塞俄比亚从4世纪开始就是一个传统基督教国家。自从约翰王的传说开始,欧洲人就认为他统治着三个印度,但他们对“印度”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模糊的。约翰王之信的作者由于缺乏对印度洋的基本知识,把埃塞俄比亚看作三者之一。当时的西方人就知道埃塞俄比亚很早就是一个基督教民族王国,但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欧洲与它的联系非常少。
其次,认为约翰王应在埃塞俄比亚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宗教认同。在中世纪晚期,耶路撒冷是欧洲与非洲之间三大交流地区之一(其他两个是南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随着十字军控制了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东方基督教文化的净土” 的城市(1099—1189年,1229—1244年),该城市受到各派督教的关注,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派。在这个教派林立的城市,十字军是否可以首次代表着基督教跨越洲际的自我觉醒还在争论之中。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地位代表着不是以种族认同而是以宗教为枢纽对“他者”的认识。①1244年耶路撒冷重新陷落后,埃塞俄比亚被欧洲人处心积虑地继续解释为欧洲以外反穆斯林战略的中心舞台。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要求约翰王重新团结在天主教会的旗帜之下,并在1300年为基督教协定拟订了计划,包括“亲爱的努比亚和上埃及其他国家的黑肤基督徒”。②
最后,还与该时期埃塞俄比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有着直接的关系。13世纪后半期,在十字军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期间,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所谓的所罗门复兴时期——扎格维王朝(Zagwe,1137—1270年)时期。其前几代君王,如耶库努·阿姆拉克(YekunoAmlak)、雅各布·塞容(YagbeSeyon,1285—1294年)等励精图治,壮大了军事实力,并加强了宗教力量,随后在东非高原实行了连续的扩张和巩固政策。强盛时期,扎格维王朝时期,基督教已经战胜了世俗权力,其统治的领域甚至超过了阿克苏姆极盛时期,并重新夺回红海贸易权。
鉴于以上原因,欧洲人在埃塞俄比亚为约翰王安置新家,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1306年,30个埃塞俄比亚大使被皇帝威德姆·阿拉德(WedemArad)派往欧洲打开了双方之间的外交来往。在他们被询问的记录中,提到他们教会的主教叫作约翰。第一个清楚描述非洲长老约翰王的是,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士约旦努斯 (Jordanus)于1329年发表的《趣闻集》中。当讨论“第三个印度”时,他记录了不少非洲大陆和国王们的趣闻逸事,并说欧洲人把他们叫作长老约翰王。③从此,非洲约翰王国的说法流行开来。
1487年和1507年,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互派使者。欧洲人加强了对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直接认识。1520年,埃塞俄比亚皇帝莱伯纳·邓格尔(LebnaDengel)与葡萄牙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这期间,约翰一直被欧洲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名字。有学者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说,埃塞俄比亚的宗教语言和上层语言中“国王”或“陛下” 可以写为Zān、ān或者ān,其发音有些像法语中的“Jean”或者意大利语中的“Gian”,都是指John。埃塞俄比亚的主教就是国王或者Zān。①尽管如此,但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人从未这样称呼自己的皇帝。
当皇帝扎拉·雅各布(ZaraYaqob)的大使于1441年参观佛罗伦萨时,当议会的高级教士坚持说他们的国王就是约翰时,他们感到很疑惑,并试图解释在一系列皇帝的名单中就没有出现过这个称呼或头衔。②然而,他们的警告没有阻止欧洲人继续这样称呼他们的皇帝。此后多年里,埃塞俄比亚都被认为是长老约翰王传说的起源地。欧洲人一厢情愿的做法是因为满足外部基督教盟友的宗教情感的需要。埃塞俄比亚是远印度或近印度,或者是第三个印度,对于欧洲人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它是基督教盟友即可。现代学者在古代资料中找不到约翰王及其国家,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也有说服力地证明,在与欧洲正式接触前,这个传说并不为埃塞俄比亚人所熟知。其实,早在18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曾否定了自己是约翰王或叫约翰的说法。捷克方济各会雷米蒂·普鲁特科(RemediusPrutky)于1751年问及皇帝伊雅苏二世(Iyasu Ⅱ)这个说法时,皇帝很吃惊,并告诉他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从不习惯自己这样被称呼。③这应该是由埃塞俄比亚君主来回答欧洲人这个传说的首次记载。当被想象的“他者”亲自站出来,澄清“自我”的真实身份时,再固执的想象者也该恍然大悟了。此后,这位神奇的约翰王只能脱下历史的外衣,进入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发挥“全能至上”的本领了。④
三、余论
从12世纪至14世纪,欧洲对约翰王的认识经历多个人物原型的变化,对其领地位置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印度到中亚,再到非洲的转换,最后只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个转换历程清晰地反映出西方对东方的认知由模糊状态中的完全想象,到逐渐修正为部分想象,最后到认识清晰下的想象褪色、消失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说,约翰王及其传说是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将东方作为他者,根据自我需求构建东方、臆想东方的结果。但是,约翰王的传说又并非子虚乌有,正如查尔斯·E.诺维尔所说,约翰王的传说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方传说与真实历史事件奇妙的调和物。①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作了长期大量的努力,探讨约翰王(或信件)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结果仍无定论。他们论争的出发点是传说或传闻与“历史事实”不能相容。然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追求绝对真实不同,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事实背后的真相。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待该问题,即是否可以把它看作中世纪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在浪漫化异域的同时,追求一种政治地理的知识,是“幻想地理”和“真实地理”的综合体。②也许约翰信件本身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表达某种观念,或描述某个真实的地理区域,而是让理想世界和现实政治观念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叙述出来。约翰王信件对其王国的描述俨然是人间天堂或上帝之城,充满着美德、正义与和谐,远优于12世纪西方腐败的基督教世界,其实这是基督教的普适主义理想的境界和象征。只不过因现实残酷的宗教斗争,这种对东方异域的浪漫化想象被西方人企图纳入自己斗争的“阵营”当中来,而少了些美好和高尚,多了些世俗和污点。
约翰王无论作为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传说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教会分裂、教俗权力之争以及十字军东征失败的年代,约翰王似乎成为了驱除伊斯兰教的象征并使欧洲人精神上有所寄托。因此,从12世纪直至美洲发现后,这个传说甚至成为欧洲思维模式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作为穆斯林后方的一个潜在的基督教盟友,为后来十字军的行动计划提供了参照,因而在欧洲的世界战略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约翰王的传说引起了欧洲人对未知领域的积极向往,刺激了欧洲君主们对海外探险的兴趣,从而推动了理大发现的到来,因而约翰王的传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当时,欧洲的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家对约翰王及其王国纷纷进行猜测。一部分人认为约翰王在印度,这可能是把他与传教士圣·托马斯混淆了。另一些人认为约翰王国应位于中亚某个未知地区的中心。上述猜测的依据是这两块地区分布有涅斯托里教派和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组织。不过,到14世纪,大部分欧洲学者已放弃了该王国在亚洲的猜想,而认为它在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王国。到16世纪末时,约翰王出现在荷兰人和德国人绘制的南部或东部非洲地图上。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德国学者为首的国际学术界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迄今不衰。概而言之,关于约翰王及其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约翰王人物原型的研究。约翰王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马可·波罗认为,蒙古草原部落克烈部首领王罕脱里才是真正的约翰王。1322—1328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岛中国旅行,把汪古部的首领当作了约翰王,并指出以往关于约翰王的种种传说不足为信。①研究该问题的先驱学者古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和弗雷德里希·赞克(FriedrichZarncke)认为,约翰王就是中亚Qara-Khitay帝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②鲁布鲁克认为,约翰王是指乃蛮部的屈出律。俄国学者布鲁恩(Ph.Bruun)于1976年提出,约翰王应在格鲁吉亚中寻找,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格鲁吉亚正在经历对穆斯林势力形成挑战的军事复兴。③M.巴伊兰(M.Bar-Ilan)则认为,约翰王信中的约翰居住在印度,而不是埃塞俄比亚。④1923年,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马里涅斯库(ConstantineMarinescu)认为约翰王的原型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1931年,意大利学者李奥纳多·奥勒斯吉(LeonardoOlschki)另辟蹊径,首先提出约翰王传说只是乌托邦。他相信,约翰王及其信件并没有历史原型,根据地理寻找他的王国毫无用处。此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如有人认为这个传说是混合了某些放纵诗人与朋友取乐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当代研究者已经放弃了固执一说的做法,而更注重对该传说历史演变的考察,例如大卫·摩尔根(DavidMorgan)考察了13世纪期间约翰王“候选人”的变化过程。⑤
第二,关于约翰王传说缘起的研究。关于该传说产生的根源,学术界的观点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寻找基督教盟友。约翰·拉纳(JohnLarner)认为,约翰王的传说表达了西方人寻找对付穆斯林的天然联盟的一种强烈愿望。①中国学者吴莉苇也认为,十字军东征时期凡有远东的军队攻打穆斯林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涉及的地理区域都被编入约翰王的故事中,那些穆斯林的敌人们就被基督徒设想为约翰王及其臣民。②瓦西里耶夫(A.A.Vasiliev)也指出,约翰王的信件于14或15世纪在俄罗斯流行也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盟友,以消除鞑靼人的威胁。③ 第二,欧洲神权与世俗权力之争的需要。例如,汉密尔顿认为,该信件是德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Barbarossa)差人伪造的,是他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斗争期间宣传的组成部分。④
第三,借以改善欧洲基督教社会道德状况。李奥纳多·奥勒斯吉认为,欧洲人虚构约翰王的目的是表达对当时欧洲基督教分裂状况的讽刺,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其目的在于改善欧洲人已经败坏的社会道德。⑤ 第三,该信件作者身份的研究。由于该信件出现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人认为约翰王“部分上是十字军想象世界的一个产物”,即此信作者应为基督教会的教士。李奥纳多·奥勒斯吉也认为其作者是西方教会的一个牧师,但他在信中只是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M.巴伊兰认为约翰王之信的作者是中世纪意大利的犹太人。⑥伯纳德·汉米尔顿(BernardHamilton)将其视为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为政治目的伪造品,可能由费雷德里克国王的大法官,科隆的大主教莱纳德·冯·达赛尔(Rainaldvon Dassel)炮制而成。⑦国内的龚缨晏先生运用中国古籍与国外学者长期研究成果相对照,对各种观点给予了评述,但并未表示支持其中的一种。⑧
二、中世纪西方对约翰王的“寻觅”
(一)雾里看花:11~12世纪,印度神奇的约翰王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西方的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为了巩固和扩大天主教的势力,极力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地中海东岸国家和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企图建立“世界教会”。然而,阿拉伯国家此时势力已经壮大起来,并对西方世界构成强大的威胁。尤其是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SeljuqTurks)占领了耶路撒冷,对教皇和基督教世界打击很大。欧洲人渴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但是多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成果,加之罗马教皇与欧洲各君主争权夺利,使整个欧洲社会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
于是,他们开始寄希望于在穆斯林世界的东面能有同盟者,约翰王的故事也就不胫而走。约翰王的原型可追溯到《新约》中的“约翰王”的提法。①在传入欧洲之前,约翰王的故事也许在亚洲的聂思脱里教派中流传已久。1122年,一名自称来自印度主教约翰(PatriarchJohn)到达罗马,要求教皇承认他的职位。这名主教约翰声称,自己所在的胡尔南(Hulna)城建在婆黑森(Phison)河边,规模和势力很大,虔诚的基督徒居住其中。城市外,十二僧侣为了纪念十二圣徒修建了圣托马斯大教堂,在他的斋戒日全亚洲的基督徒都来参观。②对此,约翰·拉纳表示:“我们面对的不过是某个自信的骗子,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制造出把戏糊弄教皇。”③ 但是,这个在东方影响力很大的基督教团体的故事还是被传播开来。
最早一份关于约翰王的记载见于德国弗赖辛(Freising)的奥托主教(BishopOtto)1145年发表的《编年史》。奥托声称亲自见到来自安条克公国的主教休(BishopHugh)向罗马教皇尤金三世(PopeEugeniusⅢ)报告说,在世界的最东方,有一名国王兼长老的约翰,是基督教徒,是《圣经》中的古代东方三博士④的直系后裔,曾打败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穆斯林国王塞米阿第(Samiardi)兄弟,并攻占了其都城埃克巴塔那(Ekbatana)。他受到祖先的激励,想到圣城耶路撒冷朝拜,但因军队无法穿越底格里斯河而退兵。根据学者的研究,休提到的这场战役可能是1141年哈喇契丹(1124—1211年,即西辽帝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Yeh-lüTa-shih,1094—1143年)与塞尔柱苏丹桑贾尔(SultanSanjar)在中亚河中地区卡特万(Oatwan)的会战,结果后者战败导致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这块地区。而耶律大石的突厥语称号“葛儿罕”(汉字又译作“古儿汗”、“菊儿罕”等),读音后讹传为希伯来文的Yohanan或叙利亚文的Yuhanan,由此再转化为拉丁文的Johannes或John。①经学者考证,耶律大石本人并非佛教徒,而是萨满教或后改信佛教徒,因而休提到的约翰王误以为是耶律大石②,但耶律大石统治部落中确有涅斯托教徒。
在1165年,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没有地址的“约翰王之信”。这位约翰王首先声明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城中的基督教徒处处受到保护”,但也有不少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民。其次自己的王国疆域广大,“统治三个印度”,“如果您确想知道我的权限范围的话,那么请您坚信,我,约翰·普里斯特的统治至高无上,其美德超群,我十分富有,统治着天下的万物生灵。” “地上蜂蜜流淌,处处都有牛奶”,“到处有着奇珍异宝”。皇宫金碧辉煌,“采用圣托马斯为King Gundoforus设计的模式建成”,经常用隆重盛大的宴会款待子民。“在这里没有做伪证者、货币伪造者、私通者或强奸者”。最后,讲述国内神奇事物。城内有亚历山大之门(theGateofAlexander)和不老泉,有一个魔镜能够看到自己统治区域的任何角落。
由此来看,约翰王及其传说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是欧洲人在没有使者或传教士亲自到亚洲考察前对东方的想象,其中的“错误”自然难免,例如信中所谓的“三个印度”③,以“近印度”向东最为突出。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印度就是世界的最东方,约翰王就是东方的统治者。这种想象很可能是根据亚洲的聂思脱里教徒或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道听途说的亚洲战事,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军事的失利需要外部帮助的需求下产生并广泛传播的。
(二)犹抱琵琶:13~14世纪,中亚草原上的约翰王
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大军的西征使东西方的碰撞与认知成为可能。随着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顺利进行,基督教徒占领了兄弟国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暴露了罗马教皇积极寻求对已知世界的封建君主的权位争夺,而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在黑海和其他东方地区“发现”了更多的基督教徒,并错误地认为穆斯林世界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超过了穆罕默德的信仰者。这无疑激发了罗马教皇更大的野心,也更加使欧洲人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位皈依基督教的约翰王将会帮助他们取得尘世和精神的巨大胜利。
13世纪初,蒙古人的迅速崛起与对外扩张是西方人始料未及的。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三次西征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对于这个彪悍、野蛮的可怕民族,西方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并企图到他们中去寻找梦寐以求的约翰王。
1221年,随十字军东征至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巴勒斯坦的阿克雷主教(BishopofAcre)德维特里(JacquesdeVitry)和西部教会的佩拉吉斯枢机(Cardinal Pelagius)向罗马报告说:“两个印度的国王”大卫王正率领着彪悍的军队帮助基督教武士们,并吞掉了强大的撒拉逊国。他是约翰王的儿子或孙子。①其实,他们所指的大卫王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因为后者在1219—1222年间攻灭了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花刺子模(Kharezm),并占领了波斯东部的呼罗珊诸地。这让欧洲的基督教徒们群情激昂,更加坚信约翰王的存在,并将之视为攻打穆斯林的天然同盟。
1240年前后,蒙古人的铁蹄踏进欧洲,使欧洲人关于约翰王的美梦变成了歌各和玛各的噩梦。其实,最早意识到蒙古人威胁的是穆斯林异端亦思马因人。他们在1238年曾向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建议结成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大同盟共同对付来自东方的可怕敌人。但是,这一建议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当时西欧教俗权力之争,尤其德皇腓特烈一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根本无暇顾及尚未成为重大威胁的蒙古人;同时蒙古人对穆斯林世界的打击,让欧洲人乐于坐山观虎斗,想渔翁得利,让“全球变得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基督”。
拔都第二次西征,饮马多瑙河,里格尼茨打败西波联军。这使西方世界惊慌失措,各种猜测随之产生。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Paris)满怀恐惧与憎恨地称,蒙古人就是《圣经》中预言的来摧毁基督子民的歌各和玛各的后代,他们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 。他认为,这也许是上帝假鞑靼人之手来惩罚他们的罪过。
与此同时,教皇格里九世呼吁组织十字军抵御蒙古人。但是,由于德皇与罗马教徒互相攻讦而流产。③1245年,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集中讨论如何防止蒙古侵略的问题。一面对防御工作,一面派遣教士充当使者,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戮基督教和侵犯欧洲,并企图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随后,罗马教会和国王纷纷派遣传教士前往寻求约翰王。其中有著名的博朗·嘉宾、阿西林使团、路布鲁克等人出使蒙古,尽管结盟的使命没有完成,但他们得知蒙古人中有不少聂斯托里教徒,使得欧洲人依然坚信在鞑靼人和穆斯林所构成的屏障以外存在约翰王的国度。
在此期间,1241年窝阔台大汗病逝,致使在欧洲征服的王子们抽兵回国,西征暂时停止。此后,蒙古人再也没有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攻势。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噩梦。于是,他们编造出各种说法来描述他们是如何打败和赶走了蒙古人。1253年,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摧毁巴格达和叙利亚,让基督教世界一片喝彩。蒙古人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认为蒙古人是伊斯兰教的天敌,是上帝的意志让穆斯林招致灭顶之灾。但是,蒙古人对待欧洲的反复无常,让他们相信,蒙古人肯定不是他们所期盼的约翰王。
在此背景下,马可·波罗的叙述充当了确认歌各和玛各之地与约翰王之国地理位置的重要角色。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从六十三章至六十七章、七十二至七十三章节中都涉及约翰王的问题。①其大体内容如下:1.鞑靼人确实是居住在北方的玛各人②。但歌各与玛各之地曾被约翰王③所征服,但现在约翰王的国土又被鞑靼人征服。2.可汗宽容那些不反对帝国臣民的各种信仰,因基督教徒战前占卜成吉思汗取胜,故优待基督教徒。3.鞑靼人与约翰王之后联姻,如成吉思汗纳王罕之女为妾,四子拖雷娶一女。而约翰国王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公主为妻。
尽管马可·波罗在该问题认识上出现了不少史实性错误,但他为鞑靼人和约翰王这原本敌对的两族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约翰王也不再是传奇中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被蒙古人打败的真实人物。最关键的是,马可·波罗认为,契丹是鞑靼人统治的约翰王之旧地,并仍有众多基督教徒生活其中。④而且,在契丹南面是居民为偶像教徒的蛮子国。⑤这使得欧洲人对“大印度”之中的“近印度”多了一些具体的知识。但在蒙古帝国瓦解后,欧洲人开始动摇这个念头:约翰王是否确实是中亚大草原上的某个国王。⑥随着13世纪末天主教派来到元朝,聂斯托里派在大草原上的历史逐渐结束,约翰王及其传说也随之淡出亚洲。
(三)蓦然回首:14~18世纪非洲的约翰王国
蒙古作为一个霸权国在亚洲的兴起以及商业在欧亚世界体系中的扩展,西方人开始意识到最遥远的亚洲内地与约翰王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是,欧洲人很快为他在未知的和神秘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个新家。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除了欧洲人对亚洲约翰王的幻想破灭外,埃塞俄比亚从4世纪开始就是一个传统基督教国家。自从约翰王的传说开始,欧洲人就认为他统治着三个印度,但他们对“印度”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模糊的。约翰王之信的作者由于缺乏对印度洋的基本知识,把埃塞俄比亚看作三者之一。当时的西方人就知道埃塞俄比亚很早就是一个基督教民族王国,但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欧洲与它的联系非常少。
其次,认为约翰王应在埃塞俄比亚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宗教认同。在中世纪晚期,耶路撒冷是欧洲与非洲之间三大交流地区之一(其他两个是南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随着十字军控制了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东方基督教文化的净土” 的城市(1099—1189年,1229—1244年),该城市受到各派督教的关注,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派。在这个教派林立的城市,十字军是否可以首次代表着基督教跨越洲际的自我觉醒还在争论之中。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地位代表着不是以种族认同而是以宗教为枢纽对“他者”的认识。①1244年耶路撒冷重新陷落后,埃塞俄比亚被欧洲人处心积虑地继续解释为欧洲以外反穆斯林战略的中心舞台。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要求约翰王重新团结在天主教会的旗帜之下,并在1300年为基督教协定拟订了计划,包括“亲爱的努比亚和上埃及其他国家的黑肤基督徒”。②
最后,还与该时期埃塞俄比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有着直接的关系。13世纪后半期,在十字军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期间,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所谓的所罗门复兴时期——扎格维王朝(Zagwe,1137—1270年)时期。其前几代君王,如耶库努·阿姆拉克(YekunoAmlak)、雅各布·塞容(YagbeSeyon,1285—1294年)等励精图治,壮大了军事实力,并加强了宗教力量,随后在东非高原实行了连续的扩张和巩固政策。强盛时期,扎格维王朝时期,基督教已经战胜了世俗权力,其统治的领域甚至超过了阿克苏姆极盛时期,并重新夺回红海贸易权。
鉴于以上原因,欧洲人在埃塞俄比亚为约翰王安置新家,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1306年,30个埃塞俄比亚大使被皇帝威德姆·阿拉德(WedemArad)派往欧洲打开了双方之间的外交来往。在他们被询问的记录中,提到他们教会的主教叫作约翰。第一个清楚描述非洲长老约翰王的是,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士约旦努斯 (Jordanus)于1329年发表的《趣闻集》中。当讨论“第三个印度”时,他记录了不少非洲大陆和国王们的趣闻逸事,并说欧洲人把他们叫作长老约翰王。③从此,非洲约翰王国的说法流行开来。
1487年和1507年,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互派使者。欧洲人加强了对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直接认识。1520年,埃塞俄比亚皇帝莱伯纳·邓格尔(LebnaDengel)与葡萄牙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这期间,约翰一直被欧洲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名字。有学者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说,埃塞俄比亚的宗教语言和上层语言中“国王”或“陛下” 可以写为Zān、ān或者ān,其发音有些像法语中的“Jean”或者意大利语中的“Gian”,都是指John。埃塞俄比亚的主教就是国王或者Zān。①尽管如此,但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人从未这样称呼自己的皇帝。
当皇帝扎拉·雅各布(ZaraYaqob)的大使于1441年参观佛罗伦萨时,当议会的高级教士坚持说他们的国王就是约翰时,他们感到很疑惑,并试图解释在一系列皇帝的名单中就没有出现过这个称呼或头衔。②然而,他们的警告没有阻止欧洲人继续这样称呼他们的皇帝。此后多年里,埃塞俄比亚都被认为是长老约翰王传说的起源地。欧洲人一厢情愿的做法是因为满足外部基督教盟友的宗教情感的需要。埃塞俄比亚是远印度或近印度,或者是第三个印度,对于欧洲人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它是基督教盟友即可。现代学者在古代资料中找不到约翰王及其国家,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也有说服力地证明,在与欧洲正式接触前,这个传说并不为埃塞俄比亚人所熟知。其实,早在18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曾否定了自己是约翰王或叫约翰的说法。捷克方济各会雷米蒂·普鲁特科(RemediusPrutky)于1751年问及皇帝伊雅苏二世(Iyasu Ⅱ)这个说法时,皇帝很吃惊,并告诉他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从不习惯自己这样被称呼。③这应该是由埃塞俄比亚君主来回答欧洲人这个传说的首次记载。当被想象的“他者”亲自站出来,澄清“自我”的真实身份时,再固执的想象者也该恍然大悟了。此后,这位神奇的约翰王只能脱下历史的外衣,进入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发挥“全能至上”的本领了。④
三、余论
从12世纪至14世纪,欧洲对约翰王的认识经历多个人物原型的变化,对其领地位置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印度到中亚,再到非洲的转换,最后只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个转换历程清晰地反映出西方对东方的认知由模糊状态中的完全想象,到逐渐修正为部分想象,最后到认识清晰下的想象褪色、消失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说,约翰王及其传说是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将东方作为他者,根据自我需求构建东方、臆想东方的结果。但是,约翰王的传说又并非子虚乌有,正如查尔斯·E.诺维尔所说,约翰王的传说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方传说与真实历史事件奇妙的调和物。①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作了长期大量的努力,探讨约翰王(或信件)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结果仍无定论。他们论争的出发点是传说或传闻与“历史事实”不能相容。然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追求绝对真实不同,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事实背后的真相。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待该问题,即是否可以把它看作中世纪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在浪漫化异域的同时,追求一种政治地理的知识,是“幻想地理”和“真实地理”的综合体。②也许约翰信件本身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表达某种观念,或描述某个真实的地理区域,而是让理想世界和现实政治观念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叙述出来。约翰王信件对其王国的描述俨然是人间天堂或上帝之城,充满着美德、正义与和谐,远优于12世纪西方腐败的基督教世界,其实这是基督教的普适主义理想的境界和象征。只不过因现实残酷的宗教斗争,这种对东方异域的浪漫化想象被西方人企图纳入自己斗争的“阵营”当中来,而少了些美好和高尚,多了些世俗和污点。
约翰王无论作为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传说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教会分裂、教俗权力之争以及十字军东征失败的年代,约翰王似乎成为了驱除伊斯兰教的象征并使欧洲人精神上有所寄托。因此,从12世纪直至美洲发现后,这个传说甚至成为欧洲思维模式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作为穆斯林后方的一个潜在的基督教盟友,为后来十字军的行动计划提供了参照,因而在欧洲的世界战略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约翰王的传说引起了欧洲人对未知领域的积极向往,刺激了欧洲君主们对海外探险的兴趣,从而推动了理大发现的到来,因而约翰王的传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附注
①然而,该信并没有地址,也没有找到关于菲利普活动的记载,其结果不得而知。
①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9页。
②古斯塔夫·奥波特和弗里德里希·赞克在19世纪晚期提出该观点,并不断地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例如Richard Hennig.Das Christentum im mittelalterlichen Asien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Saga vom Prester Johanness ,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 ⅩⅩIⅩ(1935), pp.234-252; and Terrae Incognitae, ⅡLeiden,1937, pp.361-376; L.N.Gumiev,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The Legend of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 Trans.By R.E.F.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③尽管该观点得到了亨利·裕尔和一些当代格鲁吉亚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已被弗里德里希·赞克推翻。
④ M.Bar-Ilan, Prester John: Fiction and History, History ofEuropean Ideas,20/1-3(1995), pp.291-298.
⑤David Morgan, Prester John and Mongols.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Trib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 pp.159-70.
① 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y Press,1999.
②吴梨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③ A.A.Vasiliev, Prester and Russia.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 pp.187-96.
④ Bernard Hamilton, Prester John and the Three Kings of Cologne.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pp..171-91.
⑤Charles E.Nowell, The Historical Prester John, Speculum, Vol.ⅩⅩⅤ Ⅲ, July1953, No.3,p.437.6
⑥M.Bar-Ilan, P rester John: Fiction and History' ,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20/1-3(1995), pp.291-298.David Wasserstein 认为,此信件的某些材料属于以色列十个迷失的部落,而约翰王的信件大约是在3个世纪后出现的。参见David Wasserstein,Eldad ha-Dani and Prester John.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pp..213-36.
⑦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pp..213-36.
⑧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了吴莉苇和龚缨晏教授研究成果的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①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这里的约翰王未必有其真人或拉丁名字名字是否有“Prester”之音,也许仅是后世借用说法而已。
② 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y Press.1999, p.11
③ Ibid., p.10
④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①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②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③即近印度(NearerIndia,又称“小印度”,指印度北部)、中印度、远印度(FurtherIndia,又称“大印度”,指印度南部)。
④转引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①JohnLarn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yPress,1999,p.16.
②MatthewParis,EngilshHistory,Trans.J.A.Giles,London,1852,vol.1,pp.131-132;参见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一文中对《圣经》中歌各和玛各传说和“鞑靼人”来源的解释。
③腓特烈一世抱怨本来是对付穆斯林的十字军却用来进攻神圣罗马帝国,所以鼓励了鞑靼人来进攻分裂的基督教世界;而罗马教皇则怀疑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德皇引狼入室。
①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3~147,164~173页。
②同上,第166页。“此即吾人所称峨格(Gog)同马峨格(Magog)之地”。盖在此州中有二种人,先鞑靼人居住此地,汪格人是土著,木豁勒人则为鞑靼,所以鞑靼人常自称木豁勒,而不名曰鞑靼。”
③克烈部(Kerait)首领脱忽勒王罕(TogroulWang-Khan)
④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99页。
⑤这也是17、18世纪欧洲人难于接受“契丹”就是“中国”的宗教心理因素。
⑥Silverberg.The RealmofPrester John.Ohio University Press,1996, p.139.
①Matteo Salvadore , The Ethiopian Age of Exploration:Prester John's Discovery of Europe,13061458,JournalofWorld History,December,2010,p.599.
② Hans Werner Debrunner, Presence and Prestige,Africans in Europe:A History of Africans in Europe before1918,Basel,1979,p.24.转引自Matteo Salvadore,The Ethiopian Age of Exploration:Prester John'sDiscoveryofEurope.13061458,p.599.
③Jordanus,Mirabilia, chapter Ⅵ(2).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ster_John.
①Charles E.Nowell, The Historical Prester John, Speculum, Vol.ⅩⅩⅤ Ⅲ, July1953, No.3.
② Silverberg, The Realm of Prester John.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9.
③ Arrowsmith-Brown, J .H.(translator), Prutky's trave ls to Ethiopia and other countries .London: Hakluyt Society,1991.p.115.
④约翰王的故事激起了很多文学家的创作灵感。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威廉姆·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MuchAdoAboutNothing)其中的传奇国王就是以约翰王为原型;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小说家和政治家约翰·巴肯(JohnBuchan)的第十六部书《约翰王》中采用这个传奇题材;美国的惊奇漫画系列在一系列的《神奇四侠和雷神托尔》中具有约翰王的特征。查尔斯·威廉姆斯(CharlesWilliams)在1930年的小说《战争的天堂》(WarinHeaven)让约翰王成为圣杯的弥赛亚式的保护者;约翰王及其王国在乌姆博格图·伊库(UmbertoEco)于2000年发表的小说《波多里诺》(Baudolino)中名声大噪。
①Charles E.Nowell, TheHistoricalPresterJohn, Speculum,Vol.ⅩⅩⅤ Ⅲ, July1953, No.3.
②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45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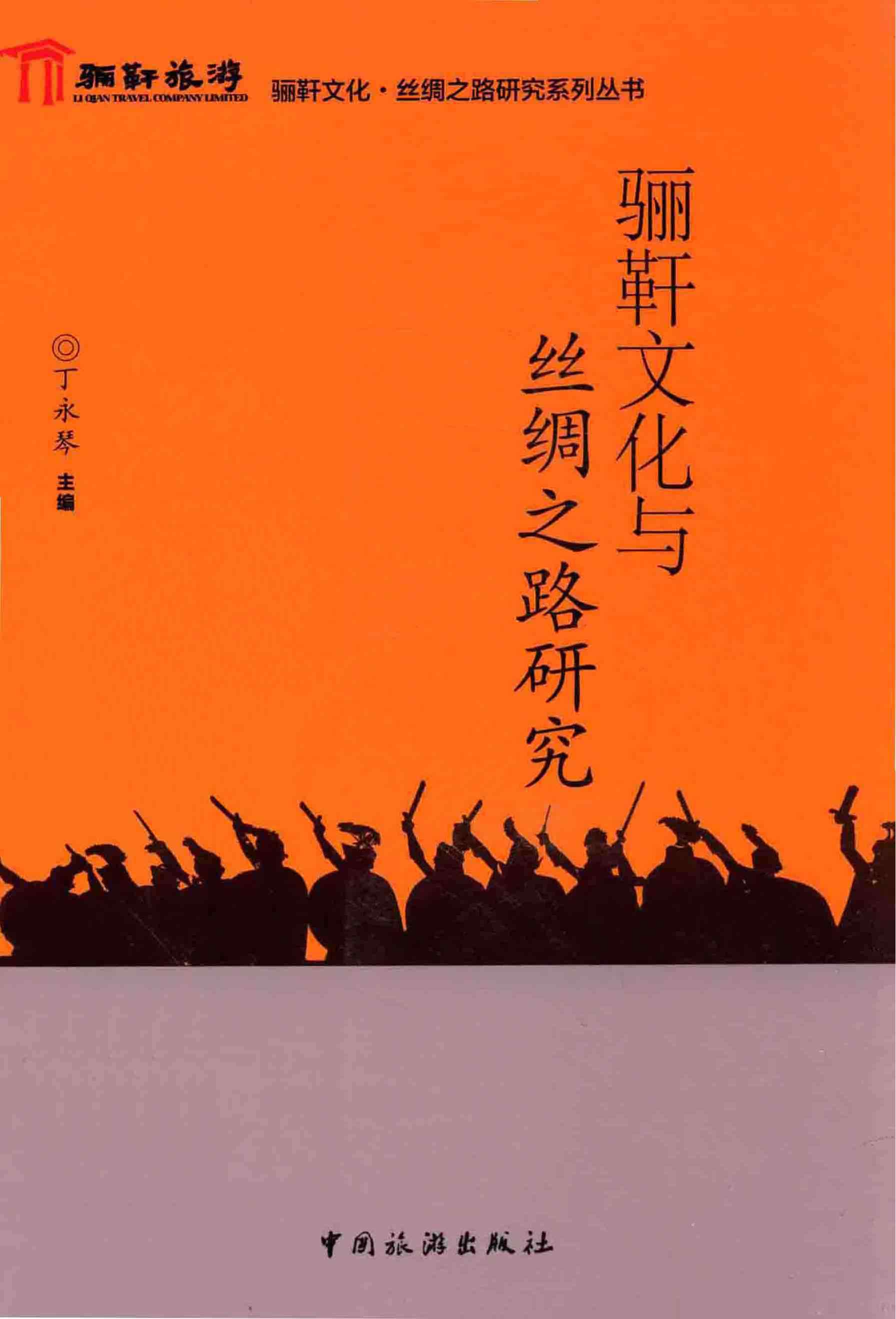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书分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骊靬文化旅游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研究、骊靬文学研究等四部分,收录了《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与战略定位》、《骊靬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展望》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姬庆红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