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研究
| 内容出处: |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36 |
| 颗粒名称: | 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研究 |
| 分类号: | K203-53 |
| 页数: | 30 |
| 页码: | 53-82 |
| 摘要: | 本文对美国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推进骊靬文化研究的开展。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
| 关键词: | 罗马军团 文化研究 历史研究 |
内容
德效骞,英文名为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于1892年3月28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Deerfield),是近代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早年跟随父母来华过颠沛流离的传教生活,青年时出于宗教热情来华当过基督教传教士,并出于传教目的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从此走上汉学研究之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 Chicago)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马歇尔学院(Marshall College)、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ofLearned Society)、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及其神学院、太平洋学会(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中研究汉学,在汉学界声誉日隆,最终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①,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他是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最早提出者,因此要厘清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渊源,他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本文对他的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推进骊靬文化研究的开展。
德效骞首次提出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时间为1940年,而不是许多论著所言的1957年。在1940年,他在杜克大学及其神学校任教,于著名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了《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AMilitaryContactbetweenChineseandRomansin36B.C.”)一文。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与另一位教授的研究有关,这位教授是荷兰汉学家戴闻达。
一、戴闻达与德效骞关于郅支之战的讨论
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一1954年),1889年出生于荷兰哈灵根(Harlingen,Netherlands),起初在莱顿大学学习荷兰语文学,不久跟随因著有六卷本《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而闻名的荷兰汉学家、人类学讲座教授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年)学习汉语,1910—1911年在巴黎又受教于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年)、高迪爱(HenriCordier,1849—1924年),奠定坚实的汉学基础。他于1912—1918年来华担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翻译,1919年在莱顿大学作为汉语讲师开始学术生涯,1930年成为莱顿大学教授,并成立汉学研究所(SinologicalInstitute)①。他因翻译《商君书》(TheBookofLordShang)和研究《道德经》而闻名,曾担任《通报》的共同主编(coeditor)②,为荷兰汉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戴闻达于1938年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十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西汉史上一次有插图的战争记载》(“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inthe 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③,该文对《汉书》中所记载的郅支之战进行了翻译,并进行了解释。该文经过充实、修改后,于1939年发表在《通报》上。这篇文章引起德效骞关注,他认为戴闻达推断出陈汤带回他进攻单于城市的图画,并且这些图画在皇帝的宴会上引起浓厚的兴趣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存在陈汤应该有描绘自己获得大胜的图画许多理由,比如陈汤有矫诏出兵之罪,他必须尽可能地取悦皇帝和宫廷以减轻罪责,于是他将图画与他的报告一起呈送朝廷,而这些图画可能会取悦于朝廷。德效骞认为在古代行军中,中国将军进入未知疆域存在绘制地图的事实,并以李陵带兵征讨匈奴为例。
当他(李陵——引者注)前行(在他被匈奴攻击之前)时,他对旅行过的地方绘图。文献(《汉书》卷54)说当他到达他的军队进入匈奴疆域最远的地方,“他停止,扎营,在地图(图)上记录山水和所经之地的构造。他派遣麾下骑兵陈步乐回(到汉人地界)以便(后者)可以报告(给武帝),送这些地图。步乐(然后)被皇帝召见”④。从这段记载,似乎制图是武帝及之后远征军的一项一般性项目,为此中国将军带着会画图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画家。如果制图是中国远征军一项公认的功能,被陈汤送回的图画的制作者可能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另一事件似乎证实这一假设:陈汤的军队没有在康居人的疆域浪费时间,而是直接进攻单于。康居人表面上敌对,因为他们与单于结盟,以至于陈汤不得不用俘获那些前来引导他的人为借口,来说明他们出现在他的军营。郅支单于已经因其横暴而得罪许多康居人,所以他们想帮助中国人,但因为他们的联盟,他们不敢公开这样做。因此在战争前极不可能的是有一个康居人在中国军营。他可能在后面跟随,但他几乎不可能画这场战争。①
从上述引文可看出,德效骞得出制作地图是汉武帝及之后中国远征军经常性的事务,由此进一步推导出,陈汤军中的画师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并以康居人因与匈奴结盟为依据证明康居人不可能是反映郅支之战图画的制作者。他认为古代中国地图上有反映地方情况的图画,由此提出从中国到康居的地图一定是一张长卷,而在两边则有许多空白之处,对这些空白之处,他认为画师会用汉军进攻郅支单于的景象来填充。
一张长途的画,从中国疆域到康居,一定是张长卷,有许多空白地方在两边,代表遥远的路途。对于一名画家而言,自然会用对单于城的辉煌进攻的激动人心的景象来填充一些空白地方。一个令人想起的例子是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他年轻时在美国政府服务,他镌刻的地图上刻上了海鸥(因此他被解雇)。因此这些地图成为陈汤送给朝廷报告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图画,当然这些图画引起家里人和宫廷妇女的关注。② 利用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的事例,他推导出画师会在地图上画上郅支之战的情景,由此陈汤上报朝廷的地图上有反映郅支之战的画,这些画引起国人和宫廷妇女的兴趣。接下来,他对戴闻达使用的一个短语提出质疑。
你(即戴闻达——引者注)翻译中的一个短语,我大胆挑战,特别是因为它加强你对图画的假设。在第259页第9行,在描绘单于门外步兵的地方,你翻译为:“lineduponeither side of the gate ina formationascloseas thescalesof afish.”在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 closeas”。我认为宁愿用“afish-scaleformation”。我由它想到希腊人重叠盾牌的行为,这叫作过度防护(Over-shielding)。这样一个战争排列自然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对他们来说它是陌生的。康居人可能从以前征服他们的希腊人那里学会它,特别是因为它曾有效地打击自己。这样一种排列无益于反对中国人的强弩,它能射穿任何盔甲。画家看见这种阵势将会把它带入画中,作为他注意到的奇异风俗的一个典型。在另一方面,它不可能进入书写的报告,因为它对没有见过它的中国人没有意义。因此这个短语“鱼鳞阵”很有可能来自一幅画而不是来自报告。我想知道如果陈汤地图上的图画不是严肃的雕刻:一系列小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分别被边界隔开,以致该系列给予战争的一系列场景。然后这个新的特征,如果有的话,在一个组成的画中对一个复杂的事件不做如此多的分析,而只是一系列画,组成一个连续,去讲一个故事,像ChinMi-ti下跪的情景和同样的人渴望地看着雕像(你的第253页底下的第4个注释)。画家自然以这种方式看一场战役。你的记载将组成半打图画。
① 他认为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closeas”,用“afish-scaleformation”即鱼鳞阵更适合原文的意思,并将鱼鳞阵与希腊人的叠盾行为相似,认为这是征服过康居的希腊人留给康居人的影响,而这种阵势无法抗击中国强弩的进攻,但却作为奇风异俗而引起中国人的注意,鱼鳞阵来自画而非报告。他认为陈汤地图上的画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讲述着郅支之战的故事。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所作的评论非常重要,接受了他关于图兼有图表、图画双重意义的说法,认为这比自己的本来想法更具说服力;同意德效骞所提出的古代地图上会在相关地方添加图画予以注释的意见,认为反映郅支之战的六幅画是一个系列,一起说明郅支之战的故事发展进程。
德效骞博士的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在这个图中确实更像兼有图表和图画的意思,这甚至比我起初的想法更令人满意。我们的古代地图不反对在它们上面对地方添加图画般的注释。我非常同意这些图画组成一组,一起说明故事的发展。这是我在论文中的意思即使我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这个意思。它们被边界隔开或它们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合成物,多种元素显示事件的连续发展。我们没有方法知道。德效骞教授的建议即步兵的鱼鳞阵势可能与希腊风格的阵法复合盾有关是特别有价值的。然后这些步兵一定是康居人而不是匈奴人。这是希腊对该地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证。②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提出的鱼鳞阵与希腊风格的复合盾阵法相关的想法非常具有价值,这是希腊文化对康居地区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当然,戴闻达并非完全赞成德效骞的想法,他认为画师不一定是中国人。不过他不会计较于画师的国籍,他认为“不管画师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幅公元前35年存在的画的事实是不同寻常的重要,它与编史的联系依然非常重要”③。
二、德效骞的《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
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据其自己交代,目的有二:一是为戴闻达教授关于郅支之战的研究提供佐证,二是更正自己之前对这场战争所发表的评论。
他在文中首先提出应该注意研究描述郅支都城的防卫者的特定词组,《汉书》中“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中的“鱼鳞阵”一词自然会提出关于能够摆出如此复杂阵势的军队的类型及其国籍的问题。
我(德效骞——引者注)提出特别的短语来研究郅支首都捍卫者的描述。中文记录描述“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现在“鱼鳞阵”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物,它自然引出关于能执行如此复杂军事策略的军队的特征和国籍问题。这些士兵必须制定这样一种方式,以便他们挤在一起并且将他们的盾重叠在一起。成功地完成这一壮举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这样有序的事情不是与匈奴一样的任何游牧民族所能够办到的),意味着较高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在这些士兵身上可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训练。牧民、蛮夷和高卢人一样混乱地冲进战争;鱼鳞阵的方式需要纪律和训练;只有职业士兵在面对攻击的时候才能成功地运用它。①
他认为鱼鳞阵是个非常复杂的阵法,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需要经过较高文明教育的士兵,而且这些士兵需要经历长期的军事训练,由此他提出这个阵法所需要的纪律和训练不是匈奴等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游牧民族不具备实践鱼鳞阵的条件,只有职业士兵才能运用它。那么职业士兵的国籍是什么呢?
我(德效骞——引者注)首先猜想这种阵势是陆龟或龟,罗马人常用来攻克堡垒。他们将盾举过头以保护他们免受飞弹落到他们身上。但是都赖水距离任何罗马领土都非常远;它在咸海东部,大约在东经71。北纬43°。即使Praaspa,公元前36年在安东尼的领导下,罗马人突破的最远的东面距离仅在东经46°。在中文记录里没有进一步提到盾在士兵头上。因此我得出结论,自从希腊人征服康居,这些士兵必定是希腊人。所以我被误导了。②
德效骞在思考鱼鳞阵时,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士兵在进攻堡垒时所用的龟甲阵 (testudo),但郅支城在都赖水旁,距离罗马帝国领土遥远,由此他排除了罗马
① HomerH.Dud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4-65.
②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p.65.
人而认为是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的可能性大,他们曾经征服康居,但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成立,并提出结论不成立的原因。
但是希腊人的大夏(Bactria)在公元前141年和前128年之间,很可能在公元前130年,大约在陈汤远征之前的一个世纪,被蛮夷打败。此外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明白在那个时候(鱼鳞阵)与马其顿方阵或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有什么关系。这或许意味着方阵在康居持续了一个世纪……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马其顿方阵扛着小的圆形盾,这使得人们无法紧密地拥挤在一起,不能出现“像鱼鳞那样排列”。①
结论不成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所建立的大夏在陈汤远征前的一个世纪即已灭亡,而且在塔恩(W.W.Tarn,1869—1957年)博士给德效骞的来信中,说明“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希腊人所拿的小型圆形盾无法使人紧密地站在一起而形成鱼鳞阵势。这样他就改变了之前关于鱼鳞阵来自希腊人的看法。然而塔恩博士在信中提到了公元前54年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士兵,从而让德效骞将鱼鳞阵的运用者重新回到了罗马人。
塔恩教授也亲切地指出,公元前54年克拉苏战败后,奥罗德斯二世 (Orodes Ⅱ)将他的罗马战俘安顿在马尔吉亚那(Margiana)(包括目前的木鹿),以守卫他的前线。一万名战俘有多少人到达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Carrhae)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们在这样的行军中难以得到善待。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娶了蛮夷妇女为妻,并在帕提亚军队中服役。有个故事,公元前36年,安东尼(Antony)在撤退时,得到克拉苏军队的一位幸存者警告和指导。他一直服役于帕提亚。这个故事不真实,叫这人为Mardian的来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但是维勒尤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和弗洛鲁斯(Florus)认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事实或许意义重大。
这些罗马人到达马尔吉亚那后做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他们曾经是军队,靠打仗谋生。希腊人、萨卡(Saca)人和其他人习惯做雇佣兵谋生。
罗马人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罗马国家能够吸收所有罗马人作战。克拉苏的人因遥远的距离和带有敌意的帕提亚人而从罗马领土分离出来了。唯一自然的是,或许这些罗马人中的一些人在机遇到来时,可能会以雇佣兵谋生。
从帕提亚边界、阿姆河(Oxus)上的马尔吉亚那边界到都赖水上的郅 支都城大约有400至500里,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人们像鱼鳞阵一样排列的时间相距有18年。如果这是罗马人的阵势,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有来自克拉苏军队的罗马军团士兵。①
德效骞综合其他学者的说法,认为卡莱战役中战败的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国王安顿在马尔吉亚那,推测他们到马尔吉亚那后会以雇佣兵为生,并认为如果《汉书》中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那么其运用者肯定是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军队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那么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吗?德效骞认为“似乎只有罗马军团的长方形盾的武器和面对弓箭罗马人的锁盾排列能称得上鱼鳞阵”,但罗马人的阵法无法对付中国人强劲的弩箭。
当中国人进入郅支城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首先在远处用弩火箭攻击该镇。任何来自克拉苏军的城外士兵自会像被帕提亚弓箭攻击的时候,很自然地重复地摆出锁盾阵形。没有任何空隙的罗马列队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列队,像一排鱼鳞。力量强大的中国弩箭射穿罗马人的盾牌和盔甲,结果这些人退到城墙后面。②
德效骞还以郅支城的建设来论证罗马军的存在。
罗马人在郅支城的真实存在被中国人发现的城外的双木栅栏(重木城——引者注)③证实。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④
德效骞认为双木栅栏(doublewoodenpalisade)是罗马人军事防御工事的典型特征,由此推断被中国发现的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证明罗马人的存在,郅支单于在建城池时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同时他论证郅支单于还需要罗马人的军事援助。郅支自然需要得到罗马人的雇佣兵。开始时他在康居国王的邀请下来到康居,然而成功驱除可怕的乌孙使他与康居国王决裂,为自己建设一座都城。他的名声让大宛(Ferghana)和其他政权向他进贡,以至于他有钱来雇用雇佣兵。另一方面,他没有大量的匈奴人,以至于他被迫依靠附近地区的人的支持。匈奴人住在现在的蒙古,由郅支的弟弟控制,他将郅支驱逐出来,以致郅支不能从那里得到增援。当他在几个康居贵族和几千驮畜的护送下带军前往康居时,郅支遭遇一场严寒,结果整个队伍中只有三千人完成这次旅程。这样他被迫依靠当地人的帮助。当他与康居国王决裂及杀害国王的女儿时,他冒犯许多康居人,因此自然地会向外寻找雇佣兵。罗马人在他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条件下,被这位著名的武士吸引,结果是相互吸引。①
德效骞认为郅支单于在与康居国王关系决裂,拥有大宛等政权进贡钱财以及他的部众因严寒而锐减、得不到匈奴其他部落的支持等情况下,他可以利用获得的钱财来雇用军事力量为己服务,而罗马人在郅支单于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前提下,答应为其服务,由此得出罗马士兵与郅支单于出于相互的需要而彼此吸引,最终走在一起。得出此结论后,德效骞又进一步地论证摆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
又一个问题排列成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我们在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信息必须靠猜想。当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他用马其顿(Macedonia)的作战方式训练当地的年轻人,结果他从印度回来时,他的总督带给他大约3万这样的年轻人。然而亚历山大有不可抵抗的征服者的声誉,反之克拉苏军团可耻地失败。人们自然不会模仿战败的流亡者的装备和作战方法。希腊国王有时也用希腊风格武装他们的国民,但这些王国是希腊人,有希腊将军。罗马的声誉如果在康居被人知道,一定在这个距离罗马帝国遥远的地方大打折扣。而且成功的龟甲阵需要相当多的技术和拥有罗马人的盾牌,我对除了专业士兵之外的任何人能够应用它表示怀疑。郅支在中国人攻击他之前待在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②
德效赛认为鱼鳞阵需要专业的士兵,技术含量高,而郅支单于来到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于是认为当地人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训练,达到运用鱼鳞阵的水平,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那么在郅支之战中,这些罗马士兵有着怎样的遭遇呢?
当城被攻击、郅支的宫殿被烧毁及其头颅被砍掉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陈汤报告总共1518人被处死(可能大部分是匈奴人),145名敌人被活捉,一千多名敌人投降。这些人被(作为奴隶)分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15个国王,他们是中国的附属国,前来起辅助作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名郅支单于的人逃掉。145名俘虏的古怪数字必定是这些罗马雇佣军的数字。中国人想要康居人保持好的印象,因此追随郅支单于的康居本地人可能被允许逃跑,投降的1000多不是康居和罗马的雇佣军。如果这些罗马人没被杀(雇佣军通常能成功地照顾好自己),他们可能被带到新疆,一些人甚至来到中国。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在郅支之战中活捉的145名俘虏是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而这些罗马士兵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那么为什么在陈汤上奏朝廷的报告中没有提起罗马人呢?
不用奇怪,陈汤和甘延寿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中没有提起任何罗马人,他们的报告成为《汉书》记载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的信息来源。只有他们中的几个人;中国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罗马,可能不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正如威尼斯人不相信马可波罗(MarcoPolo)关于中国的报告。而且陈汤写报告和送画是为了讨好中国朝廷,因为他必须为矫诏出兵远征的行为赎罪。关于一个遥远国家和几个战俘的描述无助于原谅这样的罪过。戴闻达教授已经表示郅支单于城的记录来自在该地所作的画。我们如果没有所作的画不会知道关于这个特殊军事阵形的任何事情。而且这个阵形来自这样一幅权威的画的事实证明我们将一个广泛的推论建立在单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②
德效骞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罗马,所以不可能相信罗马人的存在,于是陈汤和甘延寿的报告没有提起罗马人,而陈汤的写信与送画都是为取悦朝廷,为自己矫诏出兵赎罪,于是运用戴闻达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汉书》中关于郅支之战的记载来自画,同时鱼鳞阵这个特殊的军事阵形也来自画的事实证明其结论建立在“鱼鳞阵”这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德效骞断定公元前54年被帕提亚俘虏并迁移到马尔吉亚那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兵在康居,在公元前36年中国人进攻郅支单于都城时,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罗马人在都城的修筑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然而郅支单于的战败彻底 破坏这些痕迹,而罗马人确实与中国人发生战斗并被先进的中国武器打败①。
综上所述,德效骞在这篇文章中,说明在公元前54年于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首先被帕提亚人安置在马尔吉亚那,然后他们以雇佣兵为生,于是势单力薄的郅支单于雇用了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修筑了郅支城;在郅支之战中出现在汉军面前的“鱼鳞阵”不可能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罗马人,同时这种阵形需要严密的纪律、较高的文明和长期的训练,所以《汉书》中鱼鳞阵的运用者不可能是匈奴人和当地人,而是受雇的罗马士兵;这些罗马士兵在郅支之战中被活捉,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于此,我们可以说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说基本形成。可见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提出了罗马军团来华说,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1957年所发表的著作 《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三、德效骞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德效骞在1941年发表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中对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首先他在文中论述作为古代世界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相遇只能出现在中亚地区。
罗马人和中国人是古代世界两股最伟大的军事力量。在罗马人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an world )的时候,处于汉代(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征服他们的世界里所有值得征服的地方。如果来自这两股力量军队的相遇,可能只会出现在中亚,因为罗马的势力远远没有到达地中海的东边,而中国人几乎没有发现去帕米尔(Pamirs )以西地区的价值。这样的相遇没被注意,因为我们唯一的证据是1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单个奇怪的短语。②
德效骞认为中罗军队只能在中亚相遇的原因在于罗马人在地中海以西活动,而中国人则一般在帕米尔高原以东活动,而中罗军队在中亚的相遇以前未被世人注意,主要在于其证据只是公元1世纪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奇怪短语即“鱼鳞阵”。中罗军队的首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远征康居,进攻匈奴郅支单于的事件。
这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中国西部前沿地区(新疆)的都护做的一个事实,在他自己的职责下,一次到康居(Sogdiana )的远征取走匈奴 (Hun)郅支单于的头颅。匈奴人占领现在的蒙古(Mongolia )。匈奴王位(匈奴皇帝被称为单于)的一个竞争者,他的部落名是Luan-ti,名字是呼屠吾斯(Hu-t'u-wu-szu),统治头衔是郅支骨都侯(Chih-chihku-tu-hou),因此他一般称为郅支单于,杀死一名中国使臣,逃入西方,他被康居国王邀请前往那里,赶走入侵的游牧民族。在显耀功绩的助长下,郅支单于梦想在中亚建立一个帝国,在都赖水(怛逻斯河,Talas)边建立自己的都城,从周边部落获得贡品,一些部落也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中国的副都护陈汤看到这股新力量对中国利益的潜在危险。他集合驻扎在中国西域的军队,在当地政权的辅助下,说服他的上司随征,并出发。
军队成功地走了1000里的长途行程抵达郅支都城,在这里他们立即攻击并占领该城。这次杰出功绩的记载,最近由戴闻达博士数次提及。他表示中国人的西汉历史,我们的唯一原始资料,其信息大量来自一些被陈汤呈送给帝国朝廷的战争画。在此记录中有不同一般的评论,在攻击开始时,郅支城外有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在门的两侧。这个奇怪评论的事实来自一幅画的描述,这给它以不同寻常的可靠性。①
郅支单于在杀害汉朝使臣后,受康居国王邀请,来到康居赶走入侵康居的少数民族,在都赖水旁建立都城,其势力在中亚逐渐兴起。陈汤看到郅支单于的威胁,便集结军队远征,攻击郅支单于并占领该都城。德效骞运用戴闻达关于《汉书》对此次事件的记载来自陈汤呈送给朝廷的画的研究成果,认为100多名步兵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事实由于来自一幅画的描述,因而是可靠的。那么鱼鳞阵来自何处?
鱼鳞阵不是一种简单完成的策略。这些士兵必须挤在一起重叠他们的盾牌。这种策略需要整个群体的一致行动,特别是面对攻击的时候,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发现只有在一支专业军队中应用。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士兵据记载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以混乱的人群冲入战场。
马其顿步兵盾牌圆而小(直径只有1.5英尺),所以无法重叠它们,反之罗马军团拿着大的长方形盾牌,容易连在一起,组成一个保护层抵挡飞弹。然后我们必须寻找某种罗马人能在队列前形成类似鱼鳞的战术以及寻找位于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②
鱼鳞阵是一种复杂的阵形,需要集体的一致行动和高度的纪律性,只能在专业军队中运用,德效骞认为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军队只能是罗马和希腊,于是对希腊和罗马人的盾牌进行了比较,得出:因希腊人的盾牌圆而小,无法摆出鱼鳞阵;而罗马人的盾牌是长方形,容易拼在一起形成鱼鳞状的保护层。于是他认为鱼鳞阵来自罗马而非希腊。那么出现在中亚腹地的鱼鳞阵是罗马人提供的吗?于是他开始在中亚腹地寻找罗马军团的踪影,而在当时能够出现在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可能只有在公元前54年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旧部。于是他对卡莱战役进行描述。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带领7个军团进军帕提亚,其中4000骑兵以及同等数量的轻装士兵。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包围罗马人,整天不断发射致命的箭。罗马军团无用,因为帕提亚骑兵在他们冲锋之前撤退,结果罗马人不能抓住他们的对手。在克拉苏儿子普布利乌斯(Publius)指挥下的辅助骑兵和一些军团发动的一次决定性的冲锋,使这股力量与主力分开。为了防御帕提亚的箭,军团只能组成一个方形,环绕以锁盾。
最著名的罗马阵形是龟甲阵(testudo),在此阵中盾牌锁在一起,在城墙下开展军事行动时,用锁在一起的盾牌放在士兵头上以保护他们。似乎没有记载在这种阵形中罗马士兵也在边上锁盾。在图拉真(Trajan,98—117)纪念碑中发现的龟甲阵样式,罗马军团不仅头上有锁盾而且他们的左边也有。前进时可能难以在右边和前面锁盾,但是当站着不动时,易于形成方形锁盾。然后克拉苏军团的锁盾行动是龟甲阵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把锁盾放在头上,因为普鲁塔克(Plutarch)的原始材料陈述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的人在与主力被切断时,退到一座沙丘并锁盾,但那些人在高于沙丘处,从高于盾牌处发射,因此他们被帕提亚人射中。18年后,安东尼(Antony)的人改进他们的战术,当同样遭到帕提亚骑兵射手攻击时,前排屈膝,将盾牌放在地上,保护后面人的脚,第二排将他们的盾牌举到头的位置,其余人将盾牌举在头上,这样完成龟甲阵。用这种方法,整个军队免受帕提亚的箭,安东尼的人安全撤出。然而,克拉苏的人只是组成单边的锁盾,帕提亚人以高过外面士兵的头的轨道射箭,在自己免受危险的情况下消耗罗马的力量。
在锁盾以抵挡箭方面,希腊人和几乎其他每个人用的圆形或椭圆形盾牌是无用的,只有罗马人的长形盾是有效的,长形盾在外形上是长方形 (形状上为半圆柱形)。一排罗马长形盾在沿着前排步兵延伸得没有间隙,对于之前从未见过此种排列的人而言,看上去像鱼鳞阵,特别是因为它们的圆形表面。否则确实难以描述。
卡莱战役对罗马人是严重的灾难。在随克拉苏出发的42000人中,几乎不到1/4的人逃出。2万人被杀和1万人被俘。帕提亚人押送这些罗马囚犯去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处中亚包括现在的木鹿)去守卫他们的东部前线。1万人中有多少人到达该地,我们不知道,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在这样的征途中难以得到善待。罗马和希腊记载实际上没有关于这些人的进一步报道。贺拉斯(Horace)猜想这些罗马人与野蛮的女人结婚,在帕提亚的军队中服务。①
帕提亚的军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利用罗马军团龟甲阵的弱点,用弓箭射杀罗马士兵,并最终在卡莱战役中获胜。他们将被俘的1万名罗马囚犯押往马尔吉亚那,为其守卫东部边界。那么这些罗马战俘是怎么和郅支单于产生关系的呢?
帕提亚边界、阿姆河边的马尔吉亚那到都赖水边的郅支单于都城大约500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人在郅支城前排成鱼鳞阵时隔18年。这些罗马军团习惯于以专业士兵谋生,希望成为雇佣兵。当郅支单于在康居国王邀请下来到康居时,由康居贵族和几千驼畜护送,骑兵遇到严寒灾害,以致全部人马只有3000人度过旅程。后来郅支单于因军事成功而自满,与康居国王决裂,杀死自己的一个妻子、国王的女儿,修建自己的都城。他不能希望从匈奴获得支持——他们归于正统的单于统治,该单于是他的敌人和半个兄弟,得到中国人的支持。郅支单于由于其专横的行为也与许多康居人敌对。因此他自然会从匈奴和康居疆域之外寻找雇佣军。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白刃战战士,他们因他答应成为痛恨的帕提亚人为敌而受到著名武士的吸引。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域经郅支都城到马尔吉安那的安提阿,所以郅支崛起和他需要军队的消息自然传到罗马流亡者之中。②
德效骞认为在马尔吉亚那的罗马战俘习惯了职业兵的生活,希望成为雇佣军,而郅支单于也需要得到雇佣军的支持,因为郅支单于受康居国王之邀来康居的途中,遭遇严寒灾害而势力大减,后来又因居功自傲而与康居国王关系破裂,同时因争王位而得不到匈奴的支持。势单力孤、处境艰难的郅支单于需要雇佣军,而罗马士兵想以雇佣兵为生,于是相互吸引,在得到郅支单于关于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承诺后,他们成为位于康居的郅支单于雇佣军。德效骞认为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士兵是成为郅支单于雇佣军的克拉苏罗马军团。
在蒙古的匈奴人和帕提亚人一样,战斗时是骑兵射手,然而中国人改进弓,使用弩。一些中国古代的弩如此结实以致要拉开它们需要一个强壮的人背着地,用脚推弓,用手拉弦,这样使用他的脚、背和手臂肌肉的力量。为了控制这些弩,中国人发明不同寻常有效的扳机装置。这些弩是精密的武器,射程比任何其他军队的任何自动武器都远。它们无疑能穿透任何盾牌和盔甲。在进攻郅支城时,中国人自然开始时用一阵弩箭攻击,而他们自己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
以这种方法,中国人甚至射伤郅支单于自己的鼻子,当时他在城内的塔上向进攻者射击。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列被中国艺术家在郅支城外画出,几乎肯定是克拉苏军团的一些人,他们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被中国弩箭进攻时,他们自然重复克拉苏军队在卡莱的战术。除了拿着长形盾的罗马军团,其他士兵和武器无法产生鱼鳞阵的效果。①
德效骞认为中国的弩很厉害,能够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射箭伤敌,在中国军队发射弩箭时,罗马雇佣军重复卡莱战役的战术,摆成鱼鳞阵形。除了鱼鳞阵外,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罗马士兵的存在。
罗马人在此地的存在由双木栅栏得到确认,中国人发现城外有双木栅栏。塔恩博士(W.W.Tarn)说:“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 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被中国人在攻城时烧毁的双木栅栏可能保护郅支城外壕沟上的桥。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只在北部的蒙古由中国人的叛徒修建少数城镇,在康居郅支单于自然想要他所能发现的最好的军事工程援助,罗马军团能在筑城上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②
德效骞认为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可以证明罗马士兵的存在,并且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自身无法修筑城池,郅支城的修建得到罗马军团的帮助。
这些罗马人发生了什么?中国记载陈述当攻城时这些步兵退到城墙后。无疑他们发现中国的弩箭比在卡莱的帕提亚弓箭更有破坏性。中国记录说对于他们没有专门的更多东西。中国人的弩能从城墙上驱赶防御者,结果中国人毫不费力地横扫该城。他们烧毁郅支单于的官殿,取了他的人头,恢复死亡的中国使臣的信用。陈汤报告他处决1518人,这些人可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希望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远征的安全返回。他陈述,另外有145名敌人生俘,1000多人投降。这些人(作为奴隶)被分给西域15个政权的国王,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辅助参加远征。
145名生俘的古怪数字与列队在城外的罗马人的数字(100多)相符合。认为他们与罗马人一致有吸引力。雇佣军通常能在紧急情况下照顾好自己。因此我们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可能仍向东走,去新疆的一些政权。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进一步消息,虽然如果有人去中国很有趣,但是这样的事件似乎几乎不可能。①
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在战役中受中国弩箭的强有力攻击而不得不败退,德效骞认为他们被生俘,因为《汉书》中记载的生俘的数字(145)与在城外摆鱼鳞阵的罗马士兵数字(100多)相符合,并且推断这些罗马军团继续往东走,被作为奴隶,分给了新疆的一些政权,同时认为这些人去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
最后他总结全文,认为中国人在郅支单于的都城遇见克拉苏的罗马军团,而这些罗马士兵从帕提亚人的手中逃出,并在郅支单于的帐下当雇佣军,帮助郅支单于修筑都城;在郅支之战中,罗马军团因其人数少和中国武器先进而被俘,并被带到新疆②。
将这篇文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古》))与前文 (《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公》文)作比较,它们的内容大致一致,但又有一些区别。《公》文明显比《古》文要长,绝不是《古》文的简要版,而《古》文对《公》文在某些方面有所补充。比如补充郅支单于邀请罗马军团兵筑城的原因③,再如补充中国对俘虏的处置,德效骞认为处决1518人可能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想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安全地凯旋;145名生虏(罗马人)和1000多名降虏被分给帮助中国人远征的西域15个王做奴隶,因此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兵进一步向东方迁徙,被送到中国新疆的某个政权。但《古》文基本否定《公》文中关于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④。在结语中,不同于《公》文,德效骞提出即使在公元前1世纪,欧亚大陆间的旅行存在巨大可能性,民族间的影响也难以限制①。
四、德效骞的《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
1943年,德效骞在学术刊物《古典语言学》(ClassicalPhilology)上发表《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一文,主要是为前面两篇文章提出佐证,证明罗马与中国之间在公元前36年发生过一次军事接触,证明《汉书》中所记载的145名生虏是克拉苏罗马军团兵。他在该文中首先对之前的观点予以梳理。
前段时间我提供了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很有可能俘获100多个克拉苏军团士兵的证据。这些人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人俘获的成千上万人之一部分,并且被运送至马尔吉亚那。他们逃跑并且向东朝着中国沿着丝绸之路行走了500英里,来到正由匈奴单于郅支建设的城镇上,他们为其提供援助。一群由中国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助手陈汤领导的中国远征队,侵袭和俘获这个城镇。就目前的讲述,我将提供有关这些罗马人之后历史的证据。②
这段叙述是对德效骞前面两篇文章的总结,简要地讲述了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经过被帕提亚人运到马尔吉亚那,由此逃跑来到郅支单于的都城,并参与此城的建设,在汉军占领该城的战役中再次被俘的经过。至于其被俘之后的情况,德效骞在文中作进一步阐述。
德效骞采用戴闻达的观点,认为陈汤关于郅支之战的报告应包括一系列画,并提出这些画不同于之前的中国画。
这支远征队在许多方面很特别。陈汤关于他的战役的报告包括一系列画描述了对单于城的攻击和俘获——这在之前的中国艺术中是不为人知的。荷兰莱顿大学(LeidenUniversity)的戴闻达(Duyvendak)教授陈述说这些图画包括具有最早记录历史事件的中国绘画作品,其特点复杂,似乎有各种元素得到逐一分析,并形成了一幅混合图画。我相信这在中国艺术中是新出现的。
之前中国画利用的主题是神话、传说以及教化的奇闻逸事。这些是中国画和素描中仅保留和传下来的主题和描述。陈汤的画似乎是中国第一批描绘当代事件的绘画作品。对于朝廷来说,这些作品具有不同寻常之处,因为这些作品展示在每年的新年朝廷宴会上,甚至对于后宫的宫女们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图画。在那次远征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主题,这似乎对中国艺术来说是新东西,刺激这种变化的缘由是什么?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的画反映的是当代事件即攻击和俘获郅支单于的经过,与之前的中国画不一样,因为之前中国画的主题是神话、传说及有教化功能的奇闻逸事,同时陈汤的画还有不同寻常之处,即其在新年朝廷宴会上展示,并吸引了后宫的宫女。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在那次远征中,陈汤取得重大胜利且没有给帝国财政增加任何格外支出,比以前更进一步地将中国军队向西成功地推进,即便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还是为一个中国使者报仇,杀死闻名整个亚洲北部的匈奴武士。为了组织他的远征,他伪造了朝廷诏书,这不仅是死罪,而且拘泥于形式、信奉儒家的大臣对他也有偏见。而且他的上司——都护因拒绝迎娶宦官的姐姐而致命地冒犯了掌权的、控制政府的宦官。因此中央政府最具权力的影响人物都反对陈汤。他明白,除非他以非常生动的方式吸引朝廷对其成功的注意,否则他和甘延寿将受到惩罚。
而且陈汤不是一个自满和骄傲的中国人。他对外国的情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很想向他们学习,具有高超的想象力。他特别善于接受并且非常渴望听到任何新事物。
在这次漫长的返程中或之前,陈汤成功地召集罗马军队的领导,并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说自己的祖国。他们之前的功绩表明他们的领导必然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当时情形下(一个取胜的将军回家),很自然地将罗马凯旋行进的情况(凯旋)告诉陈汤。克拉苏的军队有部分是庞培 (Pompey)的老兵,因此这些罗马人可能目睹或参加公元前60年庞培的伟大凯旋,这仅发生在卡莱战役7年前。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场,他们也肯定从他们的同伴中听说过这一切。
使用画来表现罗马人的凯旋是众所周知的。“孔沿塔代表着被俘的城市,图画和雕塑展现战争的功绩。”在庞培的凯旋中,有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以及与他一同死去的女儿们,以及早于他死去的儿女们的图画。维斯帕先 (Vespasian)与提图斯(Titus)的凯旋中,“战争在各自的部分中由许多手法展现,提供一幅由有趣的事件构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②
德效骞首先从陈汤的处境出发来进行分析,认为陈汤虽然获得巨大胜利,但是其处境异常困难,因为矫诏出征和婚姻问题引起朝中权贵——大臣和宦官的反对,于是,陈汤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处境,必须强调自己的胜利。那么,以何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呢?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高度想象力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采取罗马军团士兵提供的信息,即使用画来表现凯旋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将陈汤的画与凯旋联系起来,这是德效骞听从哥伦比亚大学MosesHadas教授的建议的结果①。德效骞认为《汉书》对郅支之战的描述实际上是九个场景也即九幅画。下面将德效骞所描绘的九个场景与《汉书》中的文字相对照。
德效骞的描述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有少量出入,比如缺少单于在听到汉军前来的消息后,由出逃转为坚守的决策变化过程。《汉书》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①还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德效骞将《汉书》中的“重木城”翻译为“doublewooden palisade”,意思为“双木栅栏”。德效骞认为这九个来自《汉书》的场景与约瑟夫的代表作很相似,是《汉书》中唯一一次对战争的生动记录,而且中国人没有类似凯旋的活动,因而推断班固撰写《汉书》时参考了陈汤的画,陈汤画的灵感来自罗马人的凯旋。这些来自中国历史的场景与约瑟夫(Josephus)对罗马人凯旋的描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这是《汉书》中能找到的唯一一次关于战争的生动记录。班固独自编写他的历史,几乎完全来自朝廷图书馆的文件资源以及档案,可以获得关于战争的书面报告以及图画。中国人除了在胜利军队归来之时设宴庆祝的习俗,没有类似凯旋的实践活动。陈汤这样具有想象力
① 《汉书》,第9册,卷七十,第3014页。
和敏锐眼光的人,在听到罗马人的凯旋以及再现胜仗的各个场景的描述后,他很可能抓住这个特征,将之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元素,生动地描述其不同寻常的胜利以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汤送入中国朝廷的画是如此富有感情,必定来自凯旋中罗马人活动的灵感。如果这个推断被接受了,我们则可以猜测这个画家。从这些场景的特征来看,罗马人可能对这些画的主题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士兵们出现在画中,并非以不合适的方式。中国军队远征随身带着画家和制图者以保留地理和路线记录。然而,罗马指挥官可能选择当地他所熟悉的画家以准备这些场景。佛教信徒的画很可能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或许是在罗马人或陈汤或者其他中国人的建议下,由一位当地的康居人和一个中国人合作完成。①
德效骞认为虽然这些画的主题来自罗马人的指导,但是画的作者不是他们,因为罗马凯旋主要通过舞台造型或人物雕塑来表现,绘画只用于次要的场景,所以推断画的作者是中国人和康居人,他们对罗马人的做法进行了改造,改变了凯旋的表现方式②。
按照上述推理,在郅支之战中被汉军俘获的罗马士兵对陈汤讲述了罗马人庆祝胜利的方式——凯旋以及对陈汤的画造成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陈汤提供了帮助,那么陈汤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那么现在我们对罗马人的最后处置应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陈汤从罗马人获得如此有价值的援助,那么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中国历史对这145个(罗马)步兵毫无记载,仅仅说到这些俘虏被作为战利品(奴隶)分给附属政权的国王,这些国王参加了中国人的远征。而且陈汤的官方报告未提到他的收获,从其他地方,我们得知陈汤觊觎这些战利品,违背法律,在他进入中国之前,拿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该期待我们唯一的来源——历史,提到这些(罗马)俘虏,因为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而中国历史很少有关于奴隶的记载。③
德效骞认为陈汤为了报答罗马士兵所提供的帮助,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虽然《汉书》的记载提到这些俘虏作为战利品被分配给西域的政权,但是德效骞认为中国历史对奴隶不重要,所以关于这些俘虏的下落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史书,因为他认为这些罗马士兵被安置在骊靬县。
然而,我们可以很肯定地陈述这些罗马人的居住地。公元5年,朝廷地籍上列出一个名叫骊靬的城镇。这个名字与中国人用于称呼古代罗马世界的名字一样。在公元9年,中国的王位被王莽篡夺,他开始建立上帝之国,其中所有的名字都与现实相对应。他将骊靬更名为揭虏,两个汉字意味着“抚养贱民(囚犯)”和“攻下城市获得的囚犯(俘虏)”。
中国本土使用外国的地名,在汉朝,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意思——这个中国地方居住着来自国外的居民。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有两个这样命名的例子:现在陕西北部的一座城市与库车的名字相同,在陕西南部一条山脉叫做温宿。库车和温宿都位于新疆。关于这两个中国聚居地,我们特别被告知来自那些外地的居民被安置在这些中国聚居地。然后来自罗马帝国的人们几乎断定在公元5年之前就已经移民到中国,且居住在骊靬。而且,王莽的新名字说明他们是俘虏。①
德效骞认为骊靬是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而汉朝出现了以此为地名的一个城镇,这个地名在王莽建立政权后,为了表示与现实相对应,改名为“揭虏”,强烈地表示着该地的居民为囚犯(俘虏)。同时他以库车和温宿为例来说明汉朝有将外来居民安置在中国,并以该国国名命名定居地的传统。于是骊靬县的出现、骊靬为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王莽将骊靬改名为揭虏的事实以及汉朝以外国国名命名外国移民定居地的传统,成为罗马士兵移民到中国,并定居在骊靬的有力证据。这是德效骞第一次提出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骊靬的观点,此时为1943年。同时他还指出了骊靬县的方位。
古代中国骊靬位于现在永昌南部,永昌城位于甘肃省西面的一条峡谷。该地在公元前121年由中国人从匈奴人手中占领,在那个年代,其居民已经迁移至一个遥远的地方。因此该地逐渐由中国人居住。公元前79年,匈奴侵略该地区,包括骊靬附近的番和。由于骊靬在这个时代没有被提及,或许这个地方还不存在。在公元前35年,当陈汤从康居返回,这个地方很可能有部分无人居住的地区,政府想在此地区殖民,以守卫丝绸之路。到公元5年,该地区有被来自罗马领土的俘虏居住。班固详细记录了中国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除了跟随陈汤的队伍外,没有任何情况能让这么多罗马俘虏进入中国。②
骊靬县位于今永昌县南部,他认为陈汤从康居回来时,该地有部分无人居住区,政府想在此殖民,目的是守卫丝绸之路,于是公元5年被汉朝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此,这也是班固在详细记录公元前1世纪中国历史时没有提及罗马俘虏进入中国的原因所在。
德效骞在文章末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帕提亚人有效地阻止了罗马通往中国之路。任何罗马人能穿越他们的领土的唯一途径是作为战争囚犯的俘虏。位于帕提亚和中国之间的部落只允许小群的商人通过,而阻止任何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的军队护送。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从罗马移民进入中国,唯一能克服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中国西部骊靬的存在很好地证明陈汤确实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以及他把他们带入中国,并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古代中国称呼罗马世界为骊靬的地方。而且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的内容,并且开创后来以画的形式记录战役的惯例,这个惯例起源于罗马的凯旋。①
德效骞认为罗马人进入中国要经过两者之间的帕提亚以及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而帕提亚人不允许罗马人穿越他们的领土,除非作为战俘,同时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也不允许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军队的保护,唯一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他认为骊靬在中国西部的存在能够说明陈汤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并将后者带入中国,安置在骊靬县,而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开创了中国画记录战役的传统。
五、德效骞的《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
德效骞于1957年在《希腊与罗马》(GreeceandRome)杂志上发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这篇文章对其以往关于罗马士兵来中国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德效骞首先依据公元5年出现骊靬地名,肯定地提出罗马人一定移民来到中国,并建立骊靬这个城市。他指出骊靬城在今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
在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和县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用非常古老的中国对罗马称呼来命名的城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他们的城市起外国的名字。在那个清单上,有1500多个城市,只有其他两个城市使用外国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居住着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得出罗马帝国的人一定移民到了中国,并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结论。
这座用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狭长的西北部。在公元前79年不存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是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的时候。也有名字由篡权者王莽命名,他用儒家思想来纠正名字,也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给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座城市他重新命名为揭虏,这个词语包含两层意思:“在占领一个地方时候拿下的胆小鬼【被俘虏】以及‘抚养的胆小鬼’。”然后,是不是中国人抓到一些罗马军团的囚犯,然后将其安置在中国西部边界以保卫边疆?①
德效骞认为公元前79年不存在骊靬城,到公元5年出现,这座城池后被王莽改名为揭虏,于是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抓到罗马军团的囚犯,将其安置在此以保卫边疆?
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有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对罗马充满仇恨,不允许罗马人大量过境,那么这些到中国境内建立骊靬城的罗马人是如何穿越帕提亚帝国的呢?德效骞提出疑问后,开始回到罗马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之中”,并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将欧陆两端联系在一起。他首先从罗马三巨头庞培、恺撒、克拉苏之间的关系讲起,认为克拉苏在三巨头中的优势是经济,而不足确是罗马人最为看重的军事。
公元前60年,在罗马,罗马元老院将凯旋授予庞培(Pompey)将军。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到罗马,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助。恺撒 (Caesar)和克拉苏(Crassus)来帮助他,并形成了第一次三人执政。恺撒在59年成为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在55年也成为执政官。后者后来成了叙利亚总督。
克拉苏对三人执政贡献了大笔资金,这是其他两个人所缺乏的,但是他们的计划所急需的。同时他最缺乏和最想得到的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军事荣耀。他来到叙利亚之后,不顾他最好的将军的建议,向帕提亚人发动战争。公元前54年,他带着42000人进军帕提亚人的领土。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并不断发射一连串致命的箭。骑在马背上的帕提亚人在罗马人上来之前撤退,,越过他们的马匹尾部发射,罗马人陷入无助境地。罗马军团只能形成一个方阵,在四周用锁盾来保护,这样就形成典型的罗马阵形——龟形阵。但是帕提亚人朝罗马人盾牌的上、下方,毫无危险地屠杀了罗马人。到傍晚,20,000人被杀死,10,000人被抓为囚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乘夜逃跑,到达叙利亚。①
克拉苏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出任叙利亚总督后,不听旁人劝告,急切地向帕提亚发动战争。结果,克拉苏打败,罗马军团有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接着德效骞对这些俘虏的下场进行考察。
我们不知道那些囚犯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迁至马尔吉亚那(Margiana),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这是中亚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的梅尔夫(Merv)。这10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的距离超过1500英里,俘虏在这样的行军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好的待遇。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古代诗人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迎娶了蛮夷妇女并服役于帕提亚军队。②
德效骞运用普林尼的说法,认为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安置在马尔吉亚那,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由是罗马人从帕提亚西部来到了东部边界,穿越了帕提亚帝国,为其进一步向东迁徙埋下伏笔。
接着,德效骞开始研究中国方面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中国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一个世纪,现在的蒙古被匈奴人占领,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人。他们的皇帝名叫单于。公元前60年,当他们的单于去世的时候,一场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导致8位请求者将自己立为单于。不久所有的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两个:单于呼韩邪(HU HANS工E)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郅支(JZH-JZH)。当郅支在战争中打败了呼韩邪,后者从中国人中寻求援助,并派他的儿子给中国帝王做随从。中国的惯例是将结盟的外国王子控制在中国朝廷,一方面是作为他父亲良好行为的人质,另一方面是向他灌输中国文化和权力。郅支也派他的儿子来到中国朝廷。呼韩邪很礼貌地请求许可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朝廷,并表示其忠诚。他得到隆重的接待。宣帝很明智地把单于作为客人,并封他为与帝王一样的级别,位于中国人的王和其他高官之上。单于被给予丰厚的礼物,两个月后被护送回内蒙古,在那里他被许可占领某些中国边远要塞。中国人支付高昂的费用以防止给匈奴人入侵中国边界。在这几年中,中国人因为呼韩邪的追随,送给他20000蒲式耳的谷物,这样他就能吸引大量的匈奴来跟从自己。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离开了蒙古,向西走去,试图与乌孙(WU SUN)联合,乌孙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或者吉尔吉斯人(Kirghiz)。然而他们杀死了郅支的大使,并将这个人的人头送到中国。郅支惊人地成功打败了乌孙的军队。但他不能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向北方前进并占领了现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国。1000英里的草原对匈奴来说不是很远,比任何蒙古人以及其他草原骑士都远。
郅支认为在这里他会安全的。他于是向中国朝廷送了一封信,要求归还他那作为人质的儿子。守卫中国宫殿的校尉,谷吉(GUJI )(中国人的姓在前面,如匈牙利一样)负责护送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到达郅支王庭时,匈奴将谷吉和他的随从杀害了。①
他讲述匈奴内部的王位之争,主要讲述呼韩邪与郅支之争。呼韩邪赢得汉朝的支持,处于逆境的郅支被迫离开蒙古,向西迁徙,试图与乌孙联合,但乌孙杀害郅支的使者,并讨好汉朝。在这种情况下,郅支打败乌孙,来到西伯利亚西部。在自认为安全的时候,他要求归还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并杀害汉朝的使者谷吉及其随从,由此与汉朝结仇。为了逃避汉朝的进攻,他又必须向更远的地方迁徙,此时他将迁徙的目的地指向了康居。
因为此时康居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康居(Sogdiana),中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郅支作为一个战士的名声很高,康居国王邀请他住在他的国家东部边界,在那郅支有着比寒冷的北方更肥沃的领土,能够保护康居免受乌孙的攻击。郅支害怕呼韩邪和中国人,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建议,签订了一个条约。康居送了数千骆驼、驴和马。然而在路上,旅行队遭受一场冻灾,只有约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康居。国王对郅支表示欢迎并尊敬地招待,与他结盟,将他的女人送给他做妻子。郅支也将他的女儿送给康居国王。郅支现在深入乌孙国内,杀害乌孙人和让乌孙人成为奴隶,赶走他们的牛羊。乌孙不得不撤退,让他们西部的300英里国土无人居住。
于是郅支变得骄傲,破坏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康居人。他为自己在都赖水(Du-lai river)边建造一座有防御工事的都城。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塔拉斯河(River Talass),它的一条支流消失在锡尔河(Jaxartes)与巴尔喀什湖(LakeBalkash)之间的沙漠中。但是丝绸之路经过塔拉斯河,中国知道这座新城。中国本部西部有一位冠以西域都护头衔的官员,他有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自动化中国军队。当都护受中国皇帝命令出征时,在那个区域的小王国派遣军队予以帮助。①
康居因为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为了自保邀请郅支到康居的东部边界居住。郅支因害怕呼韩邪与汉朝的进攻而接受了邀请。在前往途中,因为冻灾,郅支单于所部遭受巨大伤亡,只有3000人到达康居。康居国王与郅支单于结盟,并互相联姻。郅支单于帮助康居击败乌孙,但因胜而骄,破坏了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了康居国王的女儿及数百名康居人。为了自卫,他修建了都城。郅支单于势力在康居崛起的消息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地传播到西域都护的耳中。而此时的西域都护为甘延寿,副都护为陈汤。德效骞认为陈汤“有进取心,勇敢,有计谋,但是不细心”。在郅支单于势力发展的形势下,陈汤认为这很危险,必须消灭这股势力。他看到郅支单于在中亚发展一个大国的危险。他知道在本地辅助力量的帮助下,都护掌握的中国军队能够打败郅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获得安全保障,那将会太迟了。他的上级甘延寿赞同,但必须首先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远征的命令。然而陈汤指出这样一个请求会带来官方的耽搁,过于节俭的帝国朝廷将认为这样的远征太过昂贵。这时甘延寿病倒。
这对陈汤的诱惑很大。他大胆地伪造一个帝国的命令,要求臣属的政权派遣辅助力量,命令屯田的中国军队前来都护所在地开始远征。当甘延寿的健康好转,他了解到部下的行为,他感到吃惊,要求停止行动。但是事实上危险的行为即假造帝国命令的主要罪行已经犯了,不能够停止。因此在威胁和争论之下,陈汤说服他的上级来接受不灭的荣耀的机会。当一支40000人的力量集结,甘延寿和陈汤派人向东到朝廷送一个文件,谴责自己伪造帝国命令、集结帝国军队的罪过。在同一天,公元前36年的秋天,他们向西出发,前往撤回命令无法抵达的地方。②
西域都护甘延寿病倒的情况下,作为副手的陈汤矫诏出兵远征郅支,结果得到甘延寿的支持。在公元36年,他们分兵两路,穿越乌孙,来到康居,寻求敌视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的支持,并从那获悉郅支单于的情况。
接下来,德效骞开始描述郅支之战的情形。他仍坚持认为《汉书》关于郅支之战的描述来自画,但是将之前认为的九个场景变为了八个,这主要是因为他将之前的第四个场景取消了。德效骞以鱼鳞阵、重木城、图画来证明罗马军团在郅支战役中的存在。认为“‘鱼鳞阵’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如此好的鱼鳞阵势的排列需要高度水平的训练和纪律。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或任何未开化的民族一定完成不了”,在排除希腊人后,提出鱼鳞阵就是罗马的龟甲阵,摆鱼鳞阵的士兵就是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军团;重木城是郅支单于得到罗马人帮助的证据;陈汤报告中的图书说明了罗马人的影响。
他提出史书记载的145名生虏就是摆鱼鳞阵的一百多人,也就是罗马士兵,而且这些人没有投降,只是停止战斗,后跟随陈汤来华,被安置在骊靬县:“当我们将活着的145人的数字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100多的人数相比,我们几乎不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些145名罗马军团没有投降,但只是在他们的雇主被杀后停止战斗。他们可能保持阵形,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人群。他们实际上自由地选择跟随中国人。在中国罗马人相应地安置在一座专门建造的前线城市,对此中国人当然以他们对罗马的称呼——骊靬(Li-jien)命名。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县城名单中,从王莽的命名中暗示居住在此的人是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获得,被抚养,这一切足以证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①这段记述显然将来华罗马军团的处境大大改善了,由之前所述的“战俘”变成了“自由人”。
1957年发表的《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一文综合以上3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但对以前的观点有所补充和修改。该文补充145名生虏被俘时的状态,认为这些罗马军团兵并没有投降,但当他们见到雇主被杀,即停止战斗,很可能仍然保持难以对付的队列阵势。该文修改《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关于罗马战俘去向的观点,肯定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认为他们甚至自由地选择与中国人一起走,在中国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德效骞认为骊靬的郡县名称,以及王莽的命名(将骊靬改名为“揭虏”,暗指该城由攻城战中的俘虏及其后代居住),都足以说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②。
在文章末尾,德效骞得出结论: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百余克拉苏罗马军团兵相遇,并将他们带回中国。中国人使用在任何中国文献中均未发现的词语来描述那次远征中的军事布阵,这种布阵只与罗马军队专用的龟甲阵一致。中国人围攻的匈奴城周围有重木栅栏防御,这种防御方式不为中国人或希腊人所用,却常被罗马人应用。罗马人在取胜后常用图画描述战争中的场景,而在中国却从未有过,但这类图画却成为此次中国人远征报告中的组成部分。更为明显的是在公元前79年至公元5年之间,中国建立一座以中国对罗马的称呼——骊靬命名的城市,这个名称表示该城居民来自罗马帝国。①此外,7世纪时,骊靬人发汉语拼音中没有的“x 音,这也说明罗马的影响②。
1957年出版的单行本著作《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与其论文版基本一致,只是比论文版更为详细,比如详细地解释罗马人自愿选择去中国的原因:“他们逃进周边冷酷的沙漠就意味着饿死,因为他们没有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照顾自己的能力。回到帕提亚同样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是从边防卫所逃走的。中国人则欢迎这些勇敢的战士为其戍边。”③在该书中,德效骞还对骊靬城进行构想,认为它“极有可能是按照罗马的模式建造。罗马军团兵并未向中国人投降,是自由人,所以不可能都听从中国人的规矩。按照惯例,只要他们保持和平,纳税服兵役,中国政府通常听其自然。中国人肯定会派一名朝廷命官来管理该城。因为该城存在几个世纪,他们肯定准许与中国妇女结婚。不管是否有某些殖民因素的影响,该地成为一个罗马人的定居点,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罗马人的殖民地。”④此外,该书与论文版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附录中有中英文对照的《按字母次序的汉字》(“Alphabetic ChineseScript”)表。
六、结语
综上所述,德效骞从1940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57年出版著作,可见他对古罗马军团来华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分析他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德效骞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罗马军团的归宿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战俘的生死难以确定,并认为他们如果未被杀害,最大的可能是去新疆,甚至有些去中国内地;《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断定罗马战俘会照顾好自己,不会被杀害,并推断他们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某个国王做奴隶,被带到新疆,而不太可能去中国内地;《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不再考虑他们的死亡问题,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而是在雇主被杀的情况下停止战斗;强调他们不再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诸王,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向,自愿随中国人走,不是去新疆,而是被安置在为他们特设的汉张掖郡骊靬县。可见,罗马军团的待遇是越来越好,他们来中国时是自愿而非被迫,而且来华后受到礼遇,被安置在专门为他们建造的骊靬城。
(二)罗马军团的战斗力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军团兵被中国的先进武器打败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除强调中国武器先进外,还用数量少来解释罗马军团兵的战败②,《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一反前面战败的提法,称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他们的战阵让西汉联军难以对付,最终是因为雇主死亡而自动停止战斗③。可见德效骞不仅在不断地抬高罗马军团兵的战斗力,还称赞这些罗马军团兵具有良好的雇佣军职业操守。
当然,德效骞某些观点的调整是因为发现新证据,比如在《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中出现西汉设置骊靬县的新证据。这种自己根据新证据不断调整自己学术观点的行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观点的调整可能存有主观臆断的因素,比如受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西方中心观的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过,永昌虽为西北的一座小县城,但作为古骊靬县的所在地,由于德效骞的研究,以及后来者的推动,进一步成为古罗马军团在华的落脚地,因此而备受世人的关注而扬名于外。
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德效骞首次提出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时间为1940年,而不是许多论著所言的1957年。在1940年,他在杜克大学及其神学校任教,于著名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了《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AMilitaryContactbetweenChineseandRomansin36B.C.”)一文。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与另一位教授的研究有关,这位教授是荷兰汉学家戴闻达。
一、戴闻达与德效骞关于郅支之战的讨论
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一1954年),1889年出生于荷兰哈灵根(Harlingen,Netherlands),起初在莱顿大学学习荷兰语文学,不久跟随因著有六卷本《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而闻名的荷兰汉学家、人类学讲座教授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年)学习汉语,1910—1911年在巴黎又受教于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年)、高迪爱(HenriCordier,1849—1924年),奠定坚实的汉学基础。他于1912—1918年来华担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翻译,1919年在莱顿大学作为汉语讲师开始学术生涯,1930年成为莱顿大学教授,并成立汉学研究所(SinologicalInstitute)①。他因翻译《商君书》(TheBookofLordShang)和研究《道德经》而闻名,曾担任《通报》的共同主编(coeditor)②,为荷兰汉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戴闻达于1938年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十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西汉史上一次有插图的战争记载》(“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inthe 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③,该文对《汉书》中所记载的郅支之战进行了翻译,并进行了解释。该文经过充实、修改后,于1939年发表在《通报》上。这篇文章引起德效骞关注,他认为戴闻达推断出陈汤带回他进攻单于城市的图画,并且这些图画在皇帝的宴会上引起浓厚的兴趣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存在陈汤应该有描绘自己获得大胜的图画许多理由,比如陈汤有矫诏出兵之罪,他必须尽可能地取悦皇帝和宫廷以减轻罪责,于是他将图画与他的报告一起呈送朝廷,而这些图画可能会取悦于朝廷。德效骞认为在古代行军中,中国将军进入未知疆域存在绘制地图的事实,并以李陵带兵征讨匈奴为例。
当他(李陵——引者注)前行(在他被匈奴攻击之前)时,他对旅行过的地方绘图。文献(《汉书》卷54)说当他到达他的军队进入匈奴疆域最远的地方,“他停止,扎营,在地图(图)上记录山水和所经之地的构造。他派遣麾下骑兵陈步乐回(到汉人地界)以便(后者)可以报告(给武帝),送这些地图。步乐(然后)被皇帝召见”④。从这段记载,似乎制图是武帝及之后远征军的一项一般性项目,为此中国将军带着会画图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画家。如果制图是中国远征军一项公认的功能,被陈汤送回的图画的制作者可能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另一事件似乎证实这一假设:陈汤的军队没有在康居人的疆域浪费时间,而是直接进攻单于。康居人表面上敌对,因为他们与单于结盟,以至于陈汤不得不用俘获那些前来引导他的人为借口,来说明他们出现在他的军营。郅支单于已经因其横暴而得罪许多康居人,所以他们想帮助中国人,但因为他们的联盟,他们不敢公开这样做。因此在战争前极不可能的是有一个康居人在中国军营。他可能在后面跟随,但他几乎不可能画这场战争。①
从上述引文可看出,德效骞得出制作地图是汉武帝及之后中国远征军经常性的事务,由此进一步推导出,陈汤军中的画师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并以康居人因与匈奴结盟为依据证明康居人不可能是反映郅支之战图画的制作者。他认为古代中国地图上有反映地方情况的图画,由此提出从中国到康居的地图一定是一张长卷,而在两边则有许多空白之处,对这些空白之处,他认为画师会用汉军进攻郅支单于的景象来填充。
一张长途的画,从中国疆域到康居,一定是张长卷,有许多空白地方在两边,代表遥远的路途。对于一名画家而言,自然会用对单于城的辉煌进攻的激动人心的景象来填充一些空白地方。一个令人想起的例子是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他年轻时在美国政府服务,他镌刻的地图上刻上了海鸥(因此他被解雇)。因此这些地图成为陈汤送给朝廷报告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图画,当然这些图画引起家里人和宫廷妇女的关注。② 利用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的事例,他推导出画师会在地图上画上郅支之战的情景,由此陈汤上报朝廷的地图上有反映郅支之战的画,这些画引起国人和宫廷妇女的兴趣。接下来,他对戴闻达使用的一个短语提出质疑。
你(即戴闻达——引者注)翻译中的一个短语,我大胆挑战,特别是因为它加强你对图画的假设。在第259页第9行,在描绘单于门外步兵的地方,你翻译为:“lineduponeither side of the gate ina formationascloseas thescalesof afish.”在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 closeas”。我认为宁愿用“afish-scaleformation”。我由它想到希腊人重叠盾牌的行为,这叫作过度防护(Over-shielding)。这样一个战争排列自然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对他们来说它是陌生的。康居人可能从以前征服他们的希腊人那里学会它,特别是因为它曾有效地打击自己。这样一种排列无益于反对中国人的强弩,它能射穿任何盔甲。画家看见这种阵势将会把它带入画中,作为他注意到的奇异风俗的一个典型。在另一方面,它不可能进入书写的报告,因为它对没有见过它的中国人没有意义。因此这个短语“鱼鳞阵”很有可能来自一幅画而不是来自报告。我想知道如果陈汤地图上的图画不是严肃的雕刻:一系列小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分别被边界隔开,以致该系列给予战争的一系列场景。然后这个新的特征,如果有的话,在一个组成的画中对一个复杂的事件不做如此多的分析,而只是一系列画,组成一个连续,去讲一个故事,像ChinMi-ti下跪的情景和同样的人渴望地看着雕像(你的第253页底下的第4个注释)。画家自然以这种方式看一场战役。你的记载将组成半打图画。
① 他认为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closeas”,用“afish-scaleformation”即鱼鳞阵更适合原文的意思,并将鱼鳞阵与希腊人的叠盾行为相似,认为这是征服过康居的希腊人留给康居人的影响,而这种阵势无法抗击中国强弩的进攻,但却作为奇风异俗而引起中国人的注意,鱼鳞阵来自画而非报告。他认为陈汤地图上的画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讲述着郅支之战的故事。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所作的评论非常重要,接受了他关于图兼有图表、图画双重意义的说法,认为这比自己的本来想法更具说服力;同意德效骞所提出的古代地图上会在相关地方添加图画予以注释的意见,认为反映郅支之战的六幅画是一个系列,一起说明郅支之战的故事发展进程。
德效骞博士的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在这个图中确实更像兼有图表和图画的意思,这甚至比我起初的想法更令人满意。我们的古代地图不反对在它们上面对地方添加图画般的注释。我非常同意这些图画组成一组,一起说明故事的发展。这是我在论文中的意思即使我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这个意思。它们被边界隔开或它们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合成物,多种元素显示事件的连续发展。我们没有方法知道。德效骞教授的建议即步兵的鱼鳞阵势可能与希腊风格的阵法复合盾有关是特别有价值的。然后这些步兵一定是康居人而不是匈奴人。这是希腊对该地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证。②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提出的鱼鳞阵与希腊风格的复合盾阵法相关的想法非常具有价值,这是希腊文化对康居地区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当然,戴闻达并非完全赞成德效骞的想法,他认为画师不一定是中国人。不过他不会计较于画师的国籍,他认为“不管画师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幅公元前35年存在的画的事实是不同寻常的重要,它与编史的联系依然非常重要”③。
二、德效骞的《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
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据其自己交代,目的有二:一是为戴闻达教授关于郅支之战的研究提供佐证,二是更正自己之前对这场战争所发表的评论。
他在文中首先提出应该注意研究描述郅支都城的防卫者的特定词组,《汉书》中“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中的“鱼鳞阵”一词自然会提出关于能够摆出如此复杂阵势的军队的类型及其国籍的问题。
我(德效骞——引者注)提出特别的短语来研究郅支首都捍卫者的描述。中文记录描述“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现在“鱼鳞阵”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物,它自然引出关于能执行如此复杂军事策略的军队的特征和国籍问题。这些士兵必须制定这样一种方式,以便他们挤在一起并且将他们的盾重叠在一起。成功地完成这一壮举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这样有序的事情不是与匈奴一样的任何游牧民族所能够办到的),意味着较高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在这些士兵身上可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训练。牧民、蛮夷和高卢人一样混乱地冲进战争;鱼鳞阵的方式需要纪律和训练;只有职业士兵在面对攻击的时候才能成功地运用它。①
他认为鱼鳞阵是个非常复杂的阵法,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需要经过较高文明教育的士兵,而且这些士兵需要经历长期的军事训练,由此他提出这个阵法所需要的纪律和训练不是匈奴等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游牧民族不具备实践鱼鳞阵的条件,只有职业士兵才能运用它。那么职业士兵的国籍是什么呢?
我(德效骞——引者注)首先猜想这种阵势是陆龟或龟,罗马人常用来攻克堡垒。他们将盾举过头以保护他们免受飞弹落到他们身上。但是都赖水距离任何罗马领土都非常远;它在咸海东部,大约在东经71。北纬43°。即使Praaspa,公元前36年在安东尼的领导下,罗马人突破的最远的东面距离仅在东经46°。在中文记录里没有进一步提到盾在士兵头上。因此我得出结论,自从希腊人征服康居,这些士兵必定是希腊人。所以我被误导了。②
德效骞在思考鱼鳞阵时,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士兵在进攻堡垒时所用的龟甲阵 (testudo),但郅支城在都赖水旁,距离罗马帝国领土遥远,由此他排除了罗马
① HomerH.Dud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4-65.
②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p.65.
人而认为是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的可能性大,他们曾经征服康居,但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成立,并提出结论不成立的原因。
但是希腊人的大夏(Bactria)在公元前141年和前128年之间,很可能在公元前130年,大约在陈汤远征之前的一个世纪,被蛮夷打败。此外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明白在那个时候(鱼鳞阵)与马其顿方阵或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有什么关系。这或许意味着方阵在康居持续了一个世纪……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马其顿方阵扛着小的圆形盾,这使得人们无法紧密地拥挤在一起,不能出现“像鱼鳞那样排列”。①
结论不成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所建立的大夏在陈汤远征前的一个世纪即已灭亡,而且在塔恩(W.W.Tarn,1869—1957年)博士给德效骞的来信中,说明“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希腊人所拿的小型圆形盾无法使人紧密地站在一起而形成鱼鳞阵势。这样他就改变了之前关于鱼鳞阵来自希腊人的看法。然而塔恩博士在信中提到了公元前54年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士兵,从而让德效骞将鱼鳞阵的运用者重新回到了罗马人。
塔恩教授也亲切地指出,公元前54年克拉苏战败后,奥罗德斯二世 (Orodes Ⅱ)将他的罗马战俘安顿在马尔吉亚那(Margiana)(包括目前的木鹿),以守卫他的前线。一万名战俘有多少人到达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Carrhae)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们在这样的行军中难以得到善待。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娶了蛮夷妇女为妻,并在帕提亚军队中服役。有个故事,公元前36年,安东尼(Antony)在撤退时,得到克拉苏军队的一位幸存者警告和指导。他一直服役于帕提亚。这个故事不真实,叫这人为Mardian的来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但是维勒尤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和弗洛鲁斯(Florus)认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事实或许意义重大。
这些罗马人到达马尔吉亚那后做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他们曾经是军队,靠打仗谋生。希腊人、萨卡(Saca)人和其他人习惯做雇佣兵谋生。
罗马人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罗马国家能够吸收所有罗马人作战。克拉苏的人因遥远的距离和带有敌意的帕提亚人而从罗马领土分离出来了。唯一自然的是,或许这些罗马人中的一些人在机遇到来时,可能会以雇佣兵谋生。
从帕提亚边界、阿姆河(Oxus)上的马尔吉亚那边界到都赖水上的郅 支都城大约有400至500里,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人们像鱼鳞阵一样排列的时间相距有18年。如果这是罗马人的阵势,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有来自克拉苏军队的罗马军团士兵。①
德效骞综合其他学者的说法,认为卡莱战役中战败的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国王安顿在马尔吉亚那,推测他们到马尔吉亚那后会以雇佣兵为生,并认为如果《汉书》中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那么其运用者肯定是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军队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那么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吗?德效骞认为“似乎只有罗马军团的长方形盾的武器和面对弓箭罗马人的锁盾排列能称得上鱼鳞阵”,但罗马人的阵法无法对付中国人强劲的弩箭。
当中国人进入郅支城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首先在远处用弩火箭攻击该镇。任何来自克拉苏军的城外士兵自会像被帕提亚弓箭攻击的时候,很自然地重复地摆出锁盾阵形。没有任何空隙的罗马列队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列队,像一排鱼鳞。力量强大的中国弩箭射穿罗马人的盾牌和盔甲,结果这些人退到城墙后面。②
德效骞还以郅支城的建设来论证罗马军的存在。
罗马人在郅支城的真实存在被中国人发现的城外的双木栅栏(重木城——引者注)③证实。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④
德效骞认为双木栅栏(doublewoodenpalisade)是罗马人军事防御工事的典型特征,由此推断被中国发现的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证明罗马人的存在,郅支单于在建城池时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同时他论证郅支单于还需要罗马人的军事援助。郅支自然需要得到罗马人的雇佣兵。开始时他在康居国王的邀请下来到康居,然而成功驱除可怕的乌孙使他与康居国王决裂,为自己建设一座都城。他的名声让大宛(Ferghana)和其他政权向他进贡,以至于他有钱来雇用雇佣兵。另一方面,他没有大量的匈奴人,以至于他被迫依靠附近地区的人的支持。匈奴人住在现在的蒙古,由郅支的弟弟控制,他将郅支驱逐出来,以致郅支不能从那里得到增援。当他在几个康居贵族和几千驮畜的护送下带军前往康居时,郅支遭遇一场严寒,结果整个队伍中只有三千人完成这次旅程。这样他被迫依靠当地人的帮助。当他与康居国王决裂及杀害国王的女儿时,他冒犯许多康居人,因此自然地会向外寻找雇佣兵。罗马人在他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条件下,被这位著名的武士吸引,结果是相互吸引。①
德效骞认为郅支单于在与康居国王关系决裂,拥有大宛等政权进贡钱财以及他的部众因严寒而锐减、得不到匈奴其他部落的支持等情况下,他可以利用获得的钱财来雇用军事力量为己服务,而罗马人在郅支单于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前提下,答应为其服务,由此得出罗马士兵与郅支单于出于相互的需要而彼此吸引,最终走在一起。得出此结论后,德效骞又进一步地论证摆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
又一个问题排列成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我们在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信息必须靠猜想。当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他用马其顿(Macedonia)的作战方式训练当地的年轻人,结果他从印度回来时,他的总督带给他大约3万这样的年轻人。然而亚历山大有不可抵抗的征服者的声誉,反之克拉苏军团可耻地失败。人们自然不会模仿战败的流亡者的装备和作战方法。希腊国王有时也用希腊风格武装他们的国民,但这些王国是希腊人,有希腊将军。罗马的声誉如果在康居被人知道,一定在这个距离罗马帝国遥远的地方大打折扣。而且成功的龟甲阵需要相当多的技术和拥有罗马人的盾牌,我对除了专业士兵之外的任何人能够应用它表示怀疑。郅支在中国人攻击他之前待在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②
德效赛认为鱼鳞阵需要专业的士兵,技术含量高,而郅支单于来到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于是认为当地人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训练,达到运用鱼鳞阵的水平,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那么在郅支之战中,这些罗马士兵有着怎样的遭遇呢?
当城被攻击、郅支的宫殿被烧毁及其头颅被砍掉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陈汤报告总共1518人被处死(可能大部分是匈奴人),145名敌人被活捉,一千多名敌人投降。这些人被(作为奴隶)分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15个国王,他们是中国的附属国,前来起辅助作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名郅支单于的人逃掉。145名俘虏的古怪数字必定是这些罗马雇佣军的数字。中国人想要康居人保持好的印象,因此追随郅支单于的康居本地人可能被允许逃跑,投降的1000多不是康居和罗马的雇佣军。如果这些罗马人没被杀(雇佣军通常能成功地照顾好自己),他们可能被带到新疆,一些人甚至来到中国。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在郅支之战中活捉的145名俘虏是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而这些罗马士兵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那么为什么在陈汤上奏朝廷的报告中没有提起罗马人呢?
不用奇怪,陈汤和甘延寿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中没有提起任何罗马人,他们的报告成为《汉书》记载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的信息来源。只有他们中的几个人;中国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罗马,可能不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正如威尼斯人不相信马可波罗(MarcoPolo)关于中国的报告。而且陈汤写报告和送画是为了讨好中国朝廷,因为他必须为矫诏出兵远征的行为赎罪。关于一个遥远国家和几个战俘的描述无助于原谅这样的罪过。戴闻达教授已经表示郅支单于城的记录来自在该地所作的画。我们如果没有所作的画不会知道关于这个特殊军事阵形的任何事情。而且这个阵形来自这样一幅权威的画的事实证明我们将一个广泛的推论建立在单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②
德效骞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罗马,所以不可能相信罗马人的存在,于是陈汤和甘延寿的报告没有提起罗马人,而陈汤的写信与送画都是为取悦朝廷,为自己矫诏出兵赎罪,于是运用戴闻达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汉书》中关于郅支之战的记载来自画,同时鱼鳞阵这个特殊的军事阵形也来自画的事实证明其结论建立在“鱼鳞阵”这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德效骞断定公元前54年被帕提亚俘虏并迁移到马尔吉亚那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兵在康居,在公元前36年中国人进攻郅支单于都城时,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罗马人在都城的修筑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然而郅支单于的战败彻底 破坏这些痕迹,而罗马人确实与中国人发生战斗并被先进的中国武器打败①。
综上所述,德效骞在这篇文章中,说明在公元前54年于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首先被帕提亚人安置在马尔吉亚那,然后他们以雇佣兵为生,于是势单力薄的郅支单于雇用了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修筑了郅支城;在郅支之战中出现在汉军面前的“鱼鳞阵”不可能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罗马人,同时这种阵形需要严密的纪律、较高的文明和长期的训练,所以《汉书》中鱼鳞阵的运用者不可能是匈奴人和当地人,而是受雇的罗马士兵;这些罗马士兵在郅支之战中被活捉,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于此,我们可以说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说基本形成。可见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提出了罗马军团来华说,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1957年所发表的著作 《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三、德效骞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德效骞在1941年发表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中对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首先他在文中论述作为古代世界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相遇只能出现在中亚地区。
罗马人和中国人是古代世界两股最伟大的军事力量。在罗马人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an world )的时候,处于汉代(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征服他们的世界里所有值得征服的地方。如果来自这两股力量军队的相遇,可能只会出现在中亚,因为罗马的势力远远没有到达地中海的东边,而中国人几乎没有发现去帕米尔(Pamirs )以西地区的价值。这样的相遇没被注意,因为我们唯一的证据是1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单个奇怪的短语。②
德效骞认为中罗军队只能在中亚相遇的原因在于罗马人在地中海以西活动,而中国人则一般在帕米尔高原以东活动,而中罗军队在中亚的相遇以前未被世人注意,主要在于其证据只是公元1世纪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奇怪短语即“鱼鳞阵”。中罗军队的首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远征康居,进攻匈奴郅支单于的事件。
这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中国西部前沿地区(新疆)的都护做的一个事实,在他自己的职责下,一次到康居(Sogdiana )的远征取走匈奴 (Hun)郅支单于的头颅。匈奴人占领现在的蒙古(Mongolia )。匈奴王位(匈奴皇帝被称为单于)的一个竞争者,他的部落名是Luan-ti,名字是呼屠吾斯(Hu-t'u-wu-szu),统治头衔是郅支骨都侯(Chih-chihku-tu-hou),因此他一般称为郅支单于,杀死一名中国使臣,逃入西方,他被康居国王邀请前往那里,赶走入侵的游牧民族。在显耀功绩的助长下,郅支单于梦想在中亚建立一个帝国,在都赖水(怛逻斯河,Talas)边建立自己的都城,从周边部落获得贡品,一些部落也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中国的副都护陈汤看到这股新力量对中国利益的潜在危险。他集合驻扎在中国西域的军队,在当地政权的辅助下,说服他的上司随征,并出发。
军队成功地走了1000里的长途行程抵达郅支都城,在这里他们立即攻击并占领该城。这次杰出功绩的记载,最近由戴闻达博士数次提及。他表示中国人的西汉历史,我们的唯一原始资料,其信息大量来自一些被陈汤呈送给帝国朝廷的战争画。在此记录中有不同一般的评论,在攻击开始时,郅支城外有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在门的两侧。这个奇怪评论的事实来自一幅画的描述,这给它以不同寻常的可靠性。①
郅支单于在杀害汉朝使臣后,受康居国王邀请,来到康居赶走入侵康居的少数民族,在都赖水旁建立都城,其势力在中亚逐渐兴起。陈汤看到郅支单于的威胁,便集结军队远征,攻击郅支单于并占领该都城。德效骞运用戴闻达关于《汉书》对此次事件的记载来自陈汤呈送给朝廷的画的研究成果,认为100多名步兵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事实由于来自一幅画的描述,因而是可靠的。那么鱼鳞阵来自何处?
鱼鳞阵不是一种简单完成的策略。这些士兵必须挤在一起重叠他们的盾牌。这种策略需要整个群体的一致行动,特别是面对攻击的时候,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发现只有在一支专业军队中应用。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士兵据记载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以混乱的人群冲入战场。
马其顿步兵盾牌圆而小(直径只有1.5英尺),所以无法重叠它们,反之罗马军团拿着大的长方形盾牌,容易连在一起,组成一个保护层抵挡飞弹。然后我们必须寻找某种罗马人能在队列前形成类似鱼鳞的战术以及寻找位于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②
鱼鳞阵是一种复杂的阵形,需要集体的一致行动和高度的纪律性,只能在专业军队中运用,德效骞认为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军队只能是罗马和希腊,于是对希腊和罗马人的盾牌进行了比较,得出:因希腊人的盾牌圆而小,无法摆出鱼鳞阵;而罗马人的盾牌是长方形,容易拼在一起形成鱼鳞状的保护层。于是他认为鱼鳞阵来自罗马而非希腊。那么出现在中亚腹地的鱼鳞阵是罗马人提供的吗?于是他开始在中亚腹地寻找罗马军团的踪影,而在当时能够出现在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可能只有在公元前54年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旧部。于是他对卡莱战役进行描述。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带领7个军团进军帕提亚,其中4000骑兵以及同等数量的轻装士兵。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包围罗马人,整天不断发射致命的箭。罗马军团无用,因为帕提亚骑兵在他们冲锋之前撤退,结果罗马人不能抓住他们的对手。在克拉苏儿子普布利乌斯(Publius)指挥下的辅助骑兵和一些军团发动的一次决定性的冲锋,使这股力量与主力分开。为了防御帕提亚的箭,军团只能组成一个方形,环绕以锁盾。
最著名的罗马阵形是龟甲阵(testudo),在此阵中盾牌锁在一起,在城墙下开展军事行动时,用锁在一起的盾牌放在士兵头上以保护他们。似乎没有记载在这种阵形中罗马士兵也在边上锁盾。在图拉真(Trajan,98—117)纪念碑中发现的龟甲阵样式,罗马军团不仅头上有锁盾而且他们的左边也有。前进时可能难以在右边和前面锁盾,但是当站着不动时,易于形成方形锁盾。然后克拉苏军团的锁盾行动是龟甲阵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把锁盾放在头上,因为普鲁塔克(Plutarch)的原始材料陈述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的人在与主力被切断时,退到一座沙丘并锁盾,但那些人在高于沙丘处,从高于盾牌处发射,因此他们被帕提亚人射中。18年后,安东尼(Antony)的人改进他们的战术,当同样遭到帕提亚骑兵射手攻击时,前排屈膝,将盾牌放在地上,保护后面人的脚,第二排将他们的盾牌举到头的位置,其余人将盾牌举在头上,这样完成龟甲阵。用这种方法,整个军队免受帕提亚的箭,安东尼的人安全撤出。然而,克拉苏的人只是组成单边的锁盾,帕提亚人以高过外面士兵的头的轨道射箭,在自己免受危险的情况下消耗罗马的力量。
在锁盾以抵挡箭方面,希腊人和几乎其他每个人用的圆形或椭圆形盾牌是无用的,只有罗马人的长形盾是有效的,长形盾在外形上是长方形 (形状上为半圆柱形)。一排罗马长形盾在沿着前排步兵延伸得没有间隙,对于之前从未见过此种排列的人而言,看上去像鱼鳞阵,特别是因为它们的圆形表面。否则确实难以描述。
卡莱战役对罗马人是严重的灾难。在随克拉苏出发的42000人中,几乎不到1/4的人逃出。2万人被杀和1万人被俘。帕提亚人押送这些罗马囚犯去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处中亚包括现在的木鹿)去守卫他们的东部前线。1万人中有多少人到达该地,我们不知道,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在这样的征途中难以得到善待。罗马和希腊记载实际上没有关于这些人的进一步报道。贺拉斯(Horace)猜想这些罗马人与野蛮的女人结婚,在帕提亚的军队中服务。①
帕提亚的军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利用罗马军团龟甲阵的弱点,用弓箭射杀罗马士兵,并最终在卡莱战役中获胜。他们将被俘的1万名罗马囚犯押往马尔吉亚那,为其守卫东部边界。那么这些罗马战俘是怎么和郅支单于产生关系的呢?
帕提亚边界、阿姆河边的马尔吉亚那到都赖水边的郅支单于都城大约500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人在郅支城前排成鱼鳞阵时隔18年。这些罗马军团习惯于以专业士兵谋生,希望成为雇佣兵。当郅支单于在康居国王邀请下来到康居时,由康居贵族和几千驼畜护送,骑兵遇到严寒灾害,以致全部人马只有3000人度过旅程。后来郅支单于因军事成功而自满,与康居国王决裂,杀死自己的一个妻子、国王的女儿,修建自己的都城。他不能希望从匈奴获得支持——他们归于正统的单于统治,该单于是他的敌人和半个兄弟,得到中国人的支持。郅支单于由于其专横的行为也与许多康居人敌对。因此他自然会从匈奴和康居疆域之外寻找雇佣军。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白刃战战士,他们因他答应成为痛恨的帕提亚人为敌而受到著名武士的吸引。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域经郅支都城到马尔吉安那的安提阿,所以郅支崛起和他需要军队的消息自然传到罗马流亡者之中。②
德效骞认为在马尔吉亚那的罗马战俘习惯了职业兵的生活,希望成为雇佣军,而郅支单于也需要得到雇佣军的支持,因为郅支单于受康居国王之邀来康居的途中,遭遇严寒灾害而势力大减,后来又因居功自傲而与康居国王关系破裂,同时因争王位而得不到匈奴的支持。势单力孤、处境艰难的郅支单于需要雇佣军,而罗马士兵想以雇佣兵为生,于是相互吸引,在得到郅支单于关于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承诺后,他们成为位于康居的郅支单于雇佣军。德效骞认为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士兵是成为郅支单于雇佣军的克拉苏罗马军团。
在蒙古的匈奴人和帕提亚人一样,战斗时是骑兵射手,然而中国人改进弓,使用弩。一些中国古代的弩如此结实以致要拉开它们需要一个强壮的人背着地,用脚推弓,用手拉弦,这样使用他的脚、背和手臂肌肉的力量。为了控制这些弩,中国人发明不同寻常有效的扳机装置。这些弩是精密的武器,射程比任何其他军队的任何自动武器都远。它们无疑能穿透任何盾牌和盔甲。在进攻郅支城时,中国人自然开始时用一阵弩箭攻击,而他们自己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
以这种方法,中国人甚至射伤郅支单于自己的鼻子,当时他在城内的塔上向进攻者射击。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列被中国艺术家在郅支城外画出,几乎肯定是克拉苏军团的一些人,他们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被中国弩箭进攻时,他们自然重复克拉苏军队在卡莱的战术。除了拿着长形盾的罗马军团,其他士兵和武器无法产生鱼鳞阵的效果。①
德效骞认为中国的弩很厉害,能够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射箭伤敌,在中国军队发射弩箭时,罗马雇佣军重复卡莱战役的战术,摆成鱼鳞阵形。除了鱼鳞阵外,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罗马士兵的存在。
罗马人在此地的存在由双木栅栏得到确认,中国人发现城外有双木栅栏。塔恩博士(W.W.Tarn)说:“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 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被中国人在攻城时烧毁的双木栅栏可能保护郅支城外壕沟上的桥。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只在北部的蒙古由中国人的叛徒修建少数城镇,在康居郅支单于自然想要他所能发现的最好的军事工程援助,罗马军团能在筑城上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②
德效骞认为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可以证明罗马士兵的存在,并且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自身无法修筑城池,郅支城的修建得到罗马军团的帮助。
这些罗马人发生了什么?中国记载陈述当攻城时这些步兵退到城墙后。无疑他们发现中国的弩箭比在卡莱的帕提亚弓箭更有破坏性。中国记录说对于他们没有专门的更多东西。中国人的弩能从城墙上驱赶防御者,结果中国人毫不费力地横扫该城。他们烧毁郅支单于的官殿,取了他的人头,恢复死亡的中国使臣的信用。陈汤报告他处决1518人,这些人可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希望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远征的安全返回。他陈述,另外有145名敌人生俘,1000多人投降。这些人(作为奴隶)被分给西域15个政权的国王,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辅助参加远征。
145名生俘的古怪数字与列队在城外的罗马人的数字(100多)相符合。认为他们与罗马人一致有吸引力。雇佣军通常能在紧急情况下照顾好自己。因此我们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可能仍向东走,去新疆的一些政权。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进一步消息,虽然如果有人去中国很有趣,但是这样的事件似乎几乎不可能。①
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在战役中受中国弩箭的强有力攻击而不得不败退,德效骞认为他们被生俘,因为《汉书》中记载的生俘的数字(145)与在城外摆鱼鳞阵的罗马士兵数字(100多)相符合,并且推断这些罗马军团继续往东走,被作为奴隶,分给了新疆的一些政权,同时认为这些人去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
最后他总结全文,认为中国人在郅支单于的都城遇见克拉苏的罗马军团,而这些罗马士兵从帕提亚人的手中逃出,并在郅支单于的帐下当雇佣军,帮助郅支单于修筑都城;在郅支之战中,罗马军团因其人数少和中国武器先进而被俘,并被带到新疆②。
将这篇文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古》))与前文 (《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公》文)作比较,它们的内容大致一致,但又有一些区别。《公》文明显比《古》文要长,绝不是《古》文的简要版,而《古》文对《公》文在某些方面有所补充。比如补充郅支单于邀请罗马军团兵筑城的原因③,再如补充中国对俘虏的处置,德效骞认为处决1518人可能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想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安全地凯旋;145名生虏(罗马人)和1000多名降虏被分给帮助中国人远征的西域15个王做奴隶,因此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兵进一步向东方迁徙,被送到中国新疆的某个政权。但《古》文基本否定《公》文中关于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④。在结语中,不同于《公》文,德效骞提出即使在公元前1世纪,欧亚大陆间的旅行存在巨大可能性,民族间的影响也难以限制①。
四、德效骞的《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
1943年,德效骞在学术刊物《古典语言学》(ClassicalPhilology)上发表《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一文,主要是为前面两篇文章提出佐证,证明罗马与中国之间在公元前36年发生过一次军事接触,证明《汉书》中所记载的145名生虏是克拉苏罗马军团兵。他在该文中首先对之前的观点予以梳理。
前段时间我提供了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很有可能俘获100多个克拉苏军团士兵的证据。这些人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人俘获的成千上万人之一部分,并且被运送至马尔吉亚那。他们逃跑并且向东朝着中国沿着丝绸之路行走了500英里,来到正由匈奴单于郅支建设的城镇上,他们为其提供援助。一群由中国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助手陈汤领导的中国远征队,侵袭和俘获这个城镇。就目前的讲述,我将提供有关这些罗马人之后历史的证据。②
这段叙述是对德效骞前面两篇文章的总结,简要地讲述了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经过被帕提亚人运到马尔吉亚那,由此逃跑来到郅支单于的都城,并参与此城的建设,在汉军占领该城的战役中再次被俘的经过。至于其被俘之后的情况,德效骞在文中作进一步阐述。
德效骞采用戴闻达的观点,认为陈汤关于郅支之战的报告应包括一系列画,并提出这些画不同于之前的中国画。
这支远征队在许多方面很特别。陈汤关于他的战役的报告包括一系列画描述了对单于城的攻击和俘获——这在之前的中国艺术中是不为人知的。荷兰莱顿大学(LeidenUniversity)的戴闻达(Duyvendak)教授陈述说这些图画包括具有最早记录历史事件的中国绘画作品,其特点复杂,似乎有各种元素得到逐一分析,并形成了一幅混合图画。我相信这在中国艺术中是新出现的。
之前中国画利用的主题是神话、传说以及教化的奇闻逸事。这些是中国画和素描中仅保留和传下来的主题和描述。陈汤的画似乎是中国第一批描绘当代事件的绘画作品。对于朝廷来说,这些作品具有不同寻常之处,因为这些作品展示在每年的新年朝廷宴会上,甚至对于后宫的宫女们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图画。在那次远征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主题,这似乎对中国艺术来说是新东西,刺激这种变化的缘由是什么?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的画反映的是当代事件即攻击和俘获郅支单于的经过,与之前的中国画不一样,因为之前中国画的主题是神话、传说及有教化功能的奇闻逸事,同时陈汤的画还有不同寻常之处,即其在新年朝廷宴会上展示,并吸引了后宫的宫女。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在那次远征中,陈汤取得重大胜利且没有给帝国财政增加任何格外支出,比以前更进一步地将中国军队向西成功地推进,即便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还是为一个中国使者报仇,杀死闻名整个亚洲北部的匈奴武士。为了组织他的远征,他伪造了朝廷诏书,这不仅是死罪,而且拘泥于形式、信奉儒家的大臣对他也有偏见。而且他的上司——都护因拒绝迎娶宦官的姐姐而致命地冒犯了掌权的、控制政府的宦官。因此中央政府最具权力的影响人物都反对陈汤。他明白,除非他以非常生动的方式吸引朝廷对其成功的注意,否则他和甘延寿将受到惩罚。
而且陈汤不是一个自满和骄傲的中国人。他对外国的情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很想向他们学习,具有高超的想象力。他特别善于接受并且非常渴望听到任何新事物。
在这次漫长的返程中或之前,陈汤成功地召集罗马军队的领导,并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说自己的祖国。他们之前的功绩表明他们的领导必然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当时情形下(一个取胜的将军回家),很自然地将罗马凯旋行进的情况(凯旋)告诉陈汤。克拉苏的军队有部分是庞培 (Pompey)的老兵,因此这些罗马人可能目睹或参加公元前60年庞培的伟大凯旋,这仅发生在卡莱战役7年前。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场,他们也肯定从他们的同伴中听说过这一切。
使用画来表现罗马人的凯旋是众所周知的。“孔沿塔代表着被俘的城市,图画和雕塑展现战争的功绩。”在庞培的凯旋中,有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以及与他一同死去的女儿们,以及早于他死去的儿女们的图画。维斯帕先 (Vespasian)与提图斯(Titus)的凯旋中,“战争在各自的部分中由许多手法展现,提供一幅由有趣的事件构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②
德效骞首先从陈汤的处境出发来进行分析,认为陈汤虽然获得巨大胜利,但是其处境异常困难,因为矫诏出征和婚姻问题引起朝中权贵——大臣和宦官的反对,于是,陈汤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处境,必须强调自己的胜利。那么,以何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呢?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高度想象力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采取罗马军团士兵提供的信息,即使用画来表现凯旋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将陈汤的画与凯旋联系起来,这是德效骞听从哥伦比亚大学MosesHadas教授的建议的结果①。德效骞认为《汉书》对郅支之战的描述实际上是九个场景也即九幅画。下面将德效骞所描绘的九个场景与《汉书》中的文字相对照。
德效骞的描述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有少量出入,比如缺少单于在听到汉军前来的消息后,由出逃转为坚守的决策变化过程。《汉书》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①还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德效骞将《汉书》中的“重木城”翻译为“doublewooden palisade”,意思为“双木栅栏”。德效骞认为这九个来自《汉书》的场景与约瑟夫的代表作很相似,是《汉书》中唯一一次对战争的生动记录,而且中国人没有类似凯旋的活动,因而推断班固撰写《汉书》时参考了陈汤的画,陈汤画的灵感来自罗马人的凯旋。这些来自中国历史的场景与约瑟夫(Josephus)对罗马人凯旋的描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这是《汉书》中能找到的唯一一次关于战争的生动记录。班固独自编写他的历史,几乎完全来自朝廷图书馆的文件资源以及档案,可以获得关于战争的书面报告以及图画。中国人除了在胜利军队归来之时设宴庆祝的习俗,没有类似凯旋的实践活动。陈汤这样具有想象力
① 《汉书》,第9册,卷七十,第3014页。
和敏锐眼光的人,在听到罗马人的凯旋以及再现胜仗的各个场景的描述后,他很可能抓住这个特征,将之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元素,生动地描述其不同寻常的胜利以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汤送入中国朝廷的画是如此富有感情,必定来自凯旋中罗马人活动的灵感。如果这个推断被接受了,我们则可以猜测这个画家。从这些场景的特征来看,罗马人可能对这些画的主题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士兵们出现在画中,并非以不合适的方式。中国军队远征随身带着画家和制图者以保留地理和路线记录。然而,罗马指挥官可能选择当地他所熟悉的画家以准备这些场景。佛教信徒的画很可能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或许是在罗马人或陈汤或者其他中国人的建议下,由一位当地的康居人和一个中国人合作完成。①
德效骞认为虽然这些画的主题来自罗马人的指导,但是画的作者不是他们,因为罗马凯旋主要通过舞台造型或人物雕塑来表现,绘画只用于次要的场景,所以推断画的作者是中国人和康居人,他们对罗马人的做法进行了改造,改变了凯旋的表现方式②。
按照上述推理,在郅支之战中被汉军俘获的罗马士兵对陈汤讲述了罗马人庆祝胜利的方式——凯旋以及对陈汤的画造成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陈汤提供了帮助,那么陈汤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那么现在我们对罗马人的最后处置应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陈汤从罗马人获得如此有价值的援助,那么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中国历史对这145个(罗马)步兵毫无记载,仅仅说到这些俘虏被作为战利品(奴隶)分给附属政权的国王,这些国王参加了中国人的远征。而且陈汤的官方报告未提到他的收获,从其他地方,我们得知陈汤觊觎这些战利品,违背法律,在他进入中国之前,拿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该期待我们唯一的来源——历史,提到这些(罗马)俘虏,因为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而中国历史很少有关于奴隶的记载。③
德效骞认为陈汤为了报答罗马士兵所提供的帮助,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虽然《汉书》的记载提到这些俘虏作为战利品被分配给西域的政权,但是德效骞认为中国历史对奴隶不重要,所以关于这些俘虏的下落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史书,因为他认为这些罗马士兵被安置在骊靬县。
然而,我们可以很肯定地陈述这些罗马人的居住地。公元5年,朝廷地籍上列出一个名叫骊靬的城镇。这个名字与中国人用于称呼古代罗马世界的名字一样。在公元9年,中国的王位被王莽篡夺,他开始建立上帝之国,其中所有的名字都与现实相对应。他将骊靬更名为揭虏,两个汉字意味着“抚养贱民(囚犯)”和“攻下城市获得的囚犯(俘虏)”。
中国本土使用外国的地名,在汉朝,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意思——这个中国地方居住着来自国外的居民。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有两个这样命名的例子:现在陕西北部的一座城市与库车的名字相同,在陕西南部一条山脉叫做温宿。库车和温宿都位于新疆。关于这两个中国聚居地,我们特别被告知来自那些外地的居民被安置在这些中国聚居地。然后来自罗马帝国的人们几乎断定在公元5年之前就已经移民到中国,且居住在骊靬。而且,王莽的新名字说明他们是俘虏。①
德效骞认为骊靬是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而汉朝出现了以此为地名的一个城镇,这个地名在王莽建立政权后,为了表示与现实相对应,改名为“揭虏”,强烈地表示着该地的居民为囚犯(俘虏)。同时他以库车和温宿为例来说明汉朝有将外来居民安置在中国,并以该国国名命名定居地的传统。于是骊靬县的出现、骊靬为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王莽将骊靬改名为揭虏的事实以及汉朝以外国国名命名外国移民定居地的传统,成为罗马士兵移民到中国,并定居在骊靬的有力证据。这是德效骞第一次提出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骊靬的观点,此时为1943年。同时他还指出了骊靬县的方位。
古代中国骊靬位于现在永昌南部,永昌城位于甘肃省西面的一条峡谷。该地在公元前121年由中国人从匈奴人手中占领,在那个年代,其居民已经迁移至一个遥远的地方。因此该地逐渐由中国人居住。公元前79年,匈奴侵略该地区,包括骊靬附近的番和。由于骊靬在这个时代没有被提及,或许这个地方还不存在。在公元前35年,当陈汤从康居返回,这个地方很可能有部分无人居住的地区,政府想在此地区殖民,以守卫丝绸之路。到公元5年,该地区有被来自罗马领土的俘虏居住。班固详细记录了中国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除了跟随陈汤的队伍外,没有任何情况能让这么多罗马俘虏进入中国。②
骊靬县位于今永昌县南部,他认为陈汤从康居回来时,该地有部分无人居住区,政府想在此殖民,目的是守卫丝绸之路,于是公元5年被汉朝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此,这也是班固在详细记录公元前1世纪中国历史时没有提及罗马俘虏进入中国的原因所在。
德效骞在文章末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帕提亚人有效地阻止了罗马通往中国之路。任何罗马人能穿越他们的领土的唯一途径是作为战争囚犯的俘虏。位于帕提亚和中国之间的部落只允许小群的商人通过,而阻止任何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的军队护送。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从罗马移民进入中国,唯一能克服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中国西部骊靬的存在很好地证明陈汤确实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以及他把他们带入中国,并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古代中国称呼罗马世界为骊靬的地方。而且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的内容,并且开创后来以画的形式记录战役的惯例,这个惯例起源于罗马的凯旋。①
德效骞认为罗马人进入中国要经过两者之间的帕提亚以及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而帕提亚人不允许罗马人穿越他们的领土,除非作为战俘,同时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也不允许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军队的保护,唯一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他认为骊靬在中国西部的存在能够说明陈汤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并将后者带入中国,安置在骊靬县,而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开创了中国画记录战役的传统。
五、德效骞的《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
德效骞于1957年在《希腊与罗马》(GreeceandRome)杂志上发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这篇文章对其以往关于罗马士兵来中国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德效骞首先依据公元5年出现骊靬地名,肯定地提出罗马人一定移民来到中国,并建立骊靬这个城市。他指出骊靬城在今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
在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和县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用非常古老的中国对罗马称呼来命名的城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他们的城市起外国的名字。在那个清单上,有1500多个城市,只有其他两个城市使用外国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居住着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得出罗马帝国的人一定移民到了中国,并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结论。
这座用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狭长的西北部。在公元前79年不存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是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的时候。也有名字由篡权者王莽命名,他用儒家思想来纠正名字,也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给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座城市他重新命名为揭虏,这个词语包含两层意思:“在占领一个地方时候拿下的胆小鬼【被俘虏】以及‘抚养的胆小鬼’。”然后,是不是中国人抓到一些罗马军团的囚犯,然后将其安置在中国西部边界以保卫边疆?①
德效骞认为公元前79年不存在骊靬城,到公元5年出现,这座城池后被王莽改名为揭虏,于是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抓到罗马军团的囚犯,将其安置在此以保卫边疆?
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有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对罗马充满仇恨,不允许罗马人大量过境,那么这些到中国境内建立骊靬城的罗马人是如何穿越帕提亚帝国的呢?德效骞提出疑问后,开始回到罗马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之中”,并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将欧陆两端联系在一起。他首先从罗马三巨头庞培、恺撒、克拉苏之间的关系讲起,认为克拉苏在三巨头中的优势是经济,而不足确是罗马人最为看重的军事。
公元前60年,在罗马,罗马元老院将凯旋授予庞培(Pompey)将军。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到罗马,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助。恺撒 (Caesar)和克拉苏(Crassus)来帮助他,并形成了第一次三人执政。恺撒在59年成为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在55年也成为执政官。后者后来成了叙利亚总督。
克拉苏对三人执政贡献了大笔资金,这是其他两个人所缺乏的,但是他们的计划所急需的。同时他最缺乏和最想得到的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军事荣耀。他来到叙利亚之后,不顾他最好的将军的建议,向帕提亚人发动战争。公元前54年,他带着42000人进军帕提亚人的领土。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并不断发射一连串致命的箭。骑在马背上的帕提亚人在罗马人上来之前撤退,,越过他们的马匹尾部发射,罗马人陷入无助境地。罗马军团只能形成一个方阵,在四周用锁盾来保护,这样就形成典型的罗马阵形——龟形阵。但是帕提亚人朝罗马人盾牌的上、下方,毫无危险地屠杀了罗马人。到傍晚,20,000人被杀死,10,000人被抓为囚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乘夜逃跑,到达叙利亚。①
克拉苏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出任叙利亚总督后,不听旁人劝告,急切地向帕提亚发动战争。结果,克拉苏打败,罗马军团有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接着德效骞对这些俘虏的下场进行考察。
我们不知道那些囚犯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迁至马尔吉亚那(Margiana),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这是中亚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的梅尔夫(Merv)。这10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的距离超过1500英里,俘虏在这样的行军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好的待遇。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古代诗人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迎娶了蛮夷妇女并服役于帕提亚军队。②
德效骞运用普林尼的说法,认为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安置在马尔吉亚那,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由是罗马人从帕提亚西部来到了东部边界,穿越了帕提亚帝国,为其进一步向东迁徙埋下伏笔。
接着,德效骞开始研究中国方面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中国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一个世纪,现在的蒙古被匈奴人占领,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人。他们的皇帝名叫单于。公元前60年,当他们的单于去世的时候,一场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导致8位请求者将自己立为单于。不久所有的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两个:单于呼韩邪(HU HANS工E)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郅支(JZH-JZH)。当郅支在战争中打败了呼韩邪,后者从中国人中寻求援助,并派他的儿子给中国帝王做随从。中国的惯例是将结盟的外国王子控制在中国朝廷,一方面是作为他父亲良好行为的人质,另一方面是向他灌输中国文化和权力。郅支也派他的儿子来到中国朝廷。呼韩邪很礼貌地请求许可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朝廷,并表示其忠诚。他得到隆重的接待。宣帝很明智地把单于作为客人,并封他为与帝王一样的级别,位于中国人的王和其他高官之上。单于被给予丰厚的礼物,两个月后被护送回内蒙古,在那里他被许可占领某些中国边远要塞。中国人支付高昂的费用以防止给匈奴人入侵中国边界。在这几年中,中国人因为呼韩邪的追随,送给他20000蒲式耳的谷物,这样他就能吸引大量的匈奴来跟从自己。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离开了蒙古,向西走去,试图与乌孙(WU SUN)联合,乌孙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或者吉尔吉斯人(Kirghiz)。然而他们杀死了郅支的大使,并将这个人的人头送到中国。郅支惊人地成功打败了乌孙的军队。但他不能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向北方前进并占领了现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国。1000英里的草原对匈奴来说不是很远,比任何蒙古人以及其他草原骑士都远。
郅支认为在这里他会安全的。他于是向中国朝廷送了一封信,要求归还他那作为人质的儿子。守卫中国宫殿的校尉,谷吉(GUJI )(中国人的姓在前面,如匈牙利一样)负责护送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到达郅支王庭时,匈奴将谷吉和他的随从杀害了。①
他讲述匈奴内部的王位之争,主要讲述呼韩邪与郅支之争。呼韩邪赢得汉朝的支持,处于逆境的郅支被迫离开蒙古,向西迁徙,试图与乌孙联合,但乌孙杀害郅支的使者,并讨好汉朝。在这种情况下,郅支打败乌孙,来到西伯利亚西部。在自认为安全的时候,他要求归还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并杀害汉朝的使者谷吉及其随从,由此与汉朝结仇。为了逃避汉朝的进攻,他又必须向更远的地方迁徙,此时他将迁徙的目的地指向了康居。
因为此时康居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康居(Sogdiana),中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郅支作为一个战士的名声很高,康居国王邀请他住在他的国家东部边界,在那郅支有着比寒冷的北方更肥沃的领土,能够保护康居免受乌孙的攻击。郅支害怕呼韩邪和中国人,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建议,签订了一个条约。康居送了数千骆驼、驴和马。然而在路上,旅行队遭受一场冻灾,只有约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康居。国王对郅支表示欢迎并尊敬地招待,与他结盟,将他的女人送给他做妻子。郅支也将他的女儿送给康居国王。郅支现在深入乌孙国内,杀害乌孙人和让乌孙人成为奴隶,赶走他们的牛羊。乌孙不得不撤退,让他们西部的300英里国土无人居住。
于是郅支变得骄傲,破坏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康居人。他为自己在都赖水(Du-lai river)边建造一座有防御工事的都城。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塔拉斯河(River Talass),它的一条支流消失在锡尔河(Jaxartes)与巴尔喀什湖(LakeBalkash)之间的沙漠中。但是丝绸之路经过塔拉斯河,中国知道这座新城。中国本部西部有一位冠以西域都护头衔的官员,他有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自动化中国军队。当都护受中国皇帝命令出征时,在那个区域的小王国派遣军队予以帮助。①
康居因为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为了自保邀请郅支到康居的东部边界居住。郅支因害怕呼韩邪与汉朝的进攻而接受了邀请。在前往途中,因为冻灾,郅支单于所部遭受巨大伤亡,只有3000人到达康居。康居国王与郅支单于结盟,并互相联姻。郅支单于帮助康居击败乌孙,但因胜而骄,破坏了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了康居国王的女儿及数百名康居人。为了自卫,他修建了都城。郅支单于势力在康居崛起的消息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地传播到西域都护的耳中。而此时的西域都护为甘延寿,副都护为陈汤。德效骞认为陈汤“有进取心,勇敢,有计谋,但是不细心”。在郅支单于势力发展的形势下,陈汤认为这很危险,必须消灭这股势力。他看到郅支单于在中亚发展一个大国的危险。他知道在本地辅助力量的帮助下,都护掌握的中国军队能够打败郅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获得安全保障,那将会太迟了。他的上级甘延寿赞同,但必须首先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远征的命令。然而陈汤指出这样一个请求会带来官方的耽搁,过于节俭的帝国朝廷将认为这样的远征太过昂贵。这时甘延寿病倒。
这对陈汤的诱惑很大。他大胆地伪造一个帝国的命令,要求臣属的政权派遣辅助力量,命令屯田的中国军队前来都护所在地开始远征。当甘延寿的健康好转,他了解到部下的行为,他感到吃惊,要求停止行动。但是事实上危险的行为即假造帝国命令的主要罪行已经犯了,不能够停止。因此在威胁和争论之下,陈汤说服他的上级来接受不灭的荣耀的机会。当一支40000人的力量集结,甘延寿和陈汤派人向东到朝廷送一个文件,谴责自己伪造帝国命令、集结帝国军队的罪过。在同一天,公元前36年的秋天,他们向西出发,前往撤回命令无法抵达的地方。②
西域都护甘延寿病倒的情况下,作为副手的陈汤矫诏出兵远征郅支,结果得到甘延寿的支持。在公元36年,他们分兵两路,穿越乌孙,来到康居,寻求敌视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的支持,并从那获悉郅支单于的情况。
接下来,德效骞开始描述郅支之战的情形。他仍坚持认为《汉书》关于郅支之战的描述来自画,但是将之前认为的九个场景变为了八个,这主要是因为他将之前的第四个场景取消了。德效骞以鱼鳞阵、重木城、图画来证明罗马军团在郅支战役中的存在。认为“‘鱼鳞阵’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如此好的鱼鳞阵势的排列需要高度水平的训练和纪律。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或任何未开化的民族一定完成不了”,在排除希腊人后,提出鱼鳞阵就是罗马的龟甲阵,摆鱼鳞阵的士兵就是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军团;重木城是郅支单于得到罗马人帮助的证据;陈汤报告中的图书说明了罗马人的影响。
他提出史书记载的145名生虏就是摆鱼鳞阵的一百多人,也就是罗马士兵,而且这些人没有投降,只是停止战斗,后跟随陈汤来华,被安置在骊靬县:“当我们将活着的145人的数字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100多的人数相比,我们几乎不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些145名罗马军团没有投降,但只是在他们的雇主被杀后停止战斗。他们可能保持阵形,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人群。他们实际上自由地选择跟随中国人。在中国罗马人相应地安置在一座专门建造的前线城市,对此中国人当然以他们对罗马的称呼——骊靬(Li-jien)命名。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县城名单中,从王莽的命名中暗示居住在此的人是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获得,被抚养,这一切足以证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①这段记述显然将来华罗马军团的处境大大改善了,由之前所述的“战俘”变成了“自由人”。
1957年发表的《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一文综合以上3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但对以前的观点有所补充和修改。该文补充145名生虏被俘时的状态,认为这些罗马军团兵并没有投降,但当他们见到雇主被杀,即停止战斗,很可能仍然保持难以对付的队列阵势。该文修改《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关于罗马战俘去向的观点,肯定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认为他们甚至自由地选择与中国人一起走,在中国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德效骞认为骊靬的郡县名称,以及王莽的命名(将骊靬改名为“揭虏”,暗指该城由攻城战中的俘虏及其后代居住),都足以说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②。
在文章末尾,德效骞得出结论: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百余克拉苏罗马军团兵相遇,并将他们带回中国。中国人使用在任何中国文献中均未发现的词语来描述那次远征中的军事布阵,这种布阵只与罗马军队专用的龟甲阵一致。中国人围攻的匈奴城周围有重木栅栏防御,这种防御方式不为中国人或希腊人所用,却常被罗马人应用。罗马人在取胜后常用图画描述战争中的场景,而在中国却从未有过,但这类图画却成为此次中国人远征报告中的组成部分。更为明显的是在公元前79年至公元5年之间,中国建立一座以中国对罗马的称呼——骊靬命名的城市,这个名称表示该城居民来自罗马帝国。①此外,7世纪时,骊靬人发汉语拼音中没有的“x 音,这也说明罗马的影响②。
1957年出版的单行本著作《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与其论文版基本一致,只是比论文版更为详细,比如详细地解释罗马人自愿选择去中国的原因:“他们逃进周边冷酷的沙漠就意味着饿死,因为他们没有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照顾自己的能力。回到帕提亚同样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是从边防卫所逃走的。中国人则欢迎这些勇敢的战士为其戍边。”③在该书中,德效骞还对骊靬城进行构想,认为它“极有可能是按照罗马的模式建造。罗马军团兵并未向中国人投降,是自由人,所以不可能都听从中国人的规矩。按照惯例,只要他们保持和平,纳税服兵役,中国政府通常听其自然。中国人肯定会派一名朝廷命官来管理该城。因为该城存在几个世纪,他们肯定准许与中国妇女结婚。不管是否有某些殖民因素的影响,该地成为一个罗马人的定居点,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罗马人的殖民地。”④此外,该书与论文版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附录中有中英文对照的《按字母次序的汉字》(“Alphabetic ChineseScript”)表。
六、结语
综上所述,德效骞从1940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57年出版著作,可见他对古罗马军团来华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分析他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德效骞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罗马军团的归宿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战俘的生死难以确定,并认为他们如果未被杀害,最大的可能是去新疆,甚至有些去中国内地;《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断定罗马战俘会照顾好自己,不会被杀害,并推断他们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某个国王做奴隶,被带到新疆,而不太可能去中国内地;《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不再考虑他们的死亡问题,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而是在雇主被杀的情况下停止战斗;强调他们不再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诸王,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向,自愿随中国人走,不是去新疆,而是被安置在为他们特设的汉张掖郡骊靬县。可见,罗马军团的待遇是越来越好,他们来中国时是自愿而非被迫,而且来华后受到礼遇,被安置在专门为他们建造的骊靬城。
(二)罗马军团的战斗力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军团兵被中国的先进武器打败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除强调中国武器先进外,还用数量少来解释罗马军团兵的战败②,《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一反前面战败的提法,称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他们的战阵让西汉联军难以对付,最终是因为雇主死亡而自动停止战斗③。可见德效骞不仅在不断地抬高罗马军团兵的战斗力,还称赞这些罗马军团兵具有良好的雇佣军职业操守。
当然,德效骞某些观点的调整是因为发现新证据,比如在《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中出现西汉设置骊靬县的新证据。这种自己根据新证据不断调整自己学术观点的行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观点的调整可能存有主观臆断的因素,比如受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西方中心观的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过,永昌虽为西北的一座小县城,但作为古骊靬县的所在地,由于德效骞的研究,以及后来者的推动,进一步成为古罗马军团在华的落脚地,因此而备受世人的关注而扬名于外。
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附注
①L.Carrington Goodrich, Homer Dubs(1892-1969) ,Th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9,No.4(Aug.,1970),pp.889-891.
①http://www.umass.edu/wsp/sinology/persons/duyvendak.html ②http://en.wikipedia.org/wiki/J.J.L._Duyvendak
③J.J.L.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in35B.C.,ToungPao, SecondSeries,Vol.35,Livr.1/3(1939),pp.211-215.
④这段记载出自《汉书》卷54,原文为:“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① J .J .L.Duyvendak, AComment on an Illustrated Battle-Account in35B.C.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35, Livr.1/3(1939), pp.211-213.② J .J .L.Duyvendak, AComment on an I llustrated Battle -Account in35B.C.,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35, Livr.1/3(1939), p.213.
①,J.J.L.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 in35B.C.,T' oungPao, Second Series,Vol.35, Livr.1/3(1939).pp.213-214
②.J.J.L.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 in35B.C., T'oungPao, Second Series,Vol.35, Livr.1/3(1939).pp.214-215.
③J. J. L. 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 Account in35 B.C. T' oungPao, econd Series,Vol. 35, Livr. 1/3 (1939). p.2 15 .
①1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5-66.
①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6-67.
②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2.
③许多人将重木城的“重”误拼为“zhong”,在翻回英文时误译为“heavy”,而根据原意,“重”应该是拼为“chong”,英文为“double”。
④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 oung Pao, SecondSeries, Vol.36, Livr.1(1940), pp.72-73.
①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3.
②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 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73-74.
①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74-75.
②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T' 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5.
① HomerH.Dub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6.
② 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Chinese ,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322.
① 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p.322-323.
②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p.323-324.
① HomerH.Duds , An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p.324-325.
② HomerH.Duds , An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326.
①1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p.326-327.
② 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Chinese , 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p.328-329.
① HomerH.Dud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p.329-330.
②HomerH.Dud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331.Homer
③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329.
④Homer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329.
①Homer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 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330.
②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 (Jan., 1943), p.13.
① 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3.
②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3-14.
①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9.
①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ClassicalPhilology,Vol.38, No.1(Jan.,1943), p.16.
② 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6.
③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6-17.
① Homer 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 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 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7-18.
② Homer 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 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 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8.
① 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8-19.
①H.H.Dubs, ARomanCity inAncientChina , Greece and Rome, Vol.4, No.2(1957), p.139.
① 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0.②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p.140-142.
① 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andRome,Vol.4,No.2(1957), pp.142-143.
①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 No.2(1957), p.143.②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andRome,Vol.4,No.2(1957), pp.143-144.
①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Greece andRome,Vol.4, No.2(1957), p.146.
② 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6
①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p.147148.
②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8.
③HomerH.Dubs,ARomanCityinAncientChina.London:TheChinaSociety,1957, P.15.④HomerH.Dubs,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London:TheChinaSociety,1957, p.23.
① HomerH.Dub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6.
②Homer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330.
③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6.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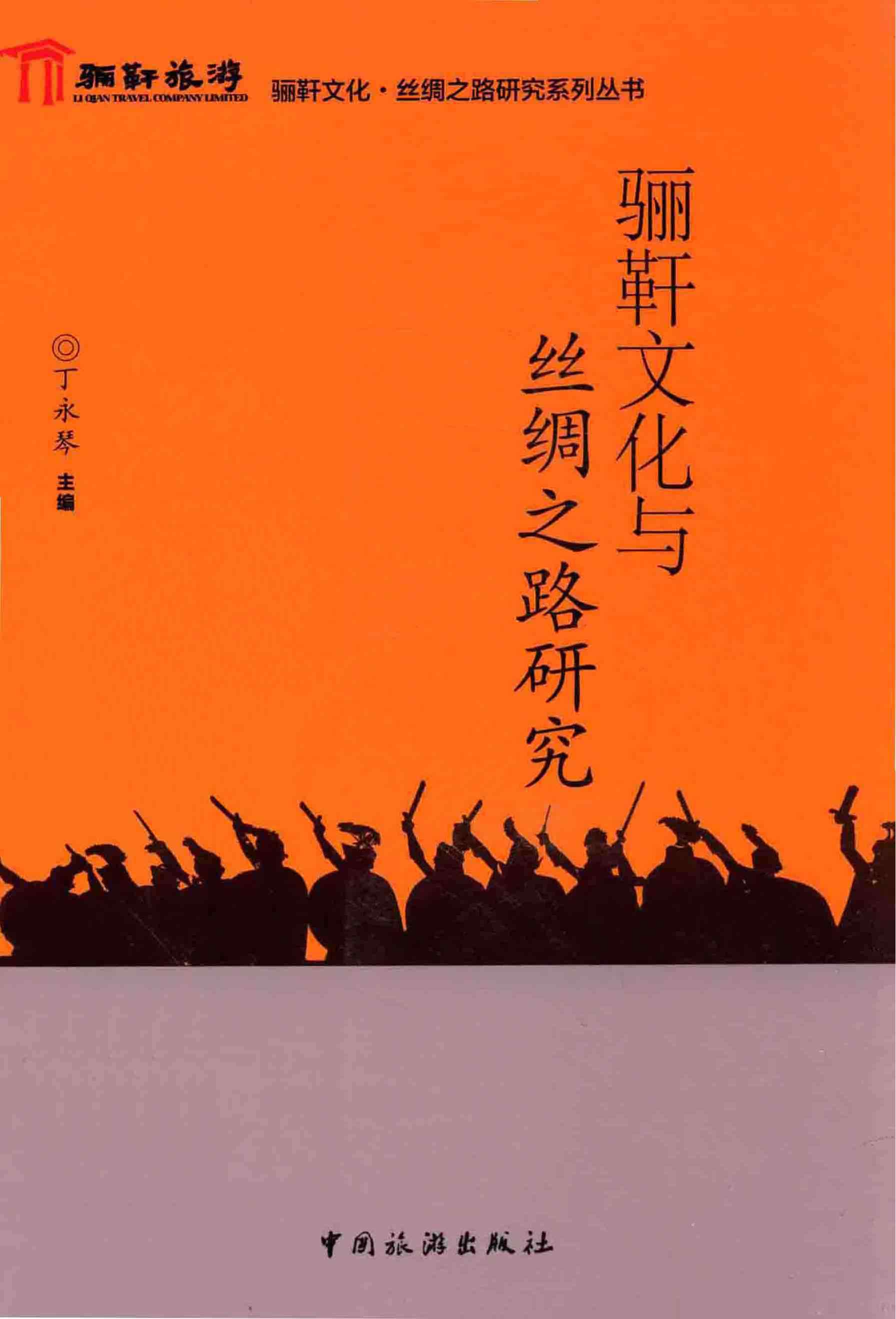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书分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骊靬文化旅游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研究、骊靬文学研究等四部分,收录了《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与战略定位》、《骊靬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展望》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刘继华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