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
| 内容出处: |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34 |
| 颗粒名称: | 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 |
| 分类号: | K203-53 |
| 页数: | 7 |
| 页码: | 42-48 |
| 摘要: | 本文论证了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 |
| 关键词: | 骊靬文化 文化研究 历史研究 |
内容
古骊靬县的建立,与陈汤俘获的那批“战俘”有关,此说,引起部分史家学者的质疑,是无可辩驳的史实。但骊靬县确为一批古罗马人而特例建置,却也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和一些历史学家的探讨,论证如下:
第一,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中国的一批权威史书,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还指出: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第二,为骊靬降人设县有据可查。《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靬说:“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师古之解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所以如此,就在于它的可靠性。师古也许料到会有人怀疑他的注释,特地向后人交代说:他的注释“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师古语)。其实,早在以前,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这“蛮族”即骊靬人。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诂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涉足骊靬者不乏其人,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靬县取骊靬国名为县名,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中国从汉、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应、颜之说,“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只是由于典籍的大量失传,我们无法看到他们考证时所根据的材料。如徐松、为嘉庆编修,因坐事戍伊犁,致力于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北史地的研究,破疑解难,成绩卓著,为世所公认。现在有人武断地说这些学者结论没有根据,未免过于草率。现在还有人说:颜师古之解始于初唐,跟西汉中期六百多年,不足为凭。如果时间能够成为理由,那么,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距西汉两千多年,距初唐1400多年,更有何资格去评说或否定颜师古搞错了呢?正因为历史遥远,大量资料在不断遗失(这一点只要看看《汉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书目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就是凤毛麟角,如同长夜里的一盏小灯,只能守护,不能把它扑灭。因此,不能否定中国从东汉初唐到清末一批学者对骊靬研究的成果。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若干现代学者在这块土地上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不仅信心十足地坚持了应劭、颜师古之说,而且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前者如向达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后者如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
第三,确有大批古罗马人生活在河西。这批古罗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靬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靬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如《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189年),朝廷徵卓为少府,卓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腹上。”这里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就是湟中羌和大秦胡之意,后面的“羌、胡”就是“湟中义从及秦胡”的概语。秦胡确指古罗马人。有人认为,此处“秦”指汉人,假设如此,那么,下句的“羌、胡敝肠狗态”作何解释?汉人到哪里去了?再如,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曹操施离间计,约韩遂“叙旧”,以引起马超疑心。《魏书》具体记下了会语的情景。《魏书》说:“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防护木栏)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这《魏书》是曹魏朝廷编撰的皇家史,成书早于《三国志》,现在我们无法看到曹魏《魏书》,但这段文字却由南朝的裴松之抄录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注释中,十分可贵。这段文字,“胡”出现两次,前面点出是秦胡,后面就省掉秦字,正好说明“秦”是对该胡属性的限定。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有“属国秦胡卢水”的记载,“秦胡”纯属为民族之称,证据充分。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西汉初个别情况下也确称汉人为秦人,但秦人和秦胡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是两个概念。古史书中将汉人和少数民族并论时,总是讲“华夷”或“夏夷”,从未有过“秦夷”之称。那种把“秦胡”认为是汉、胡之合称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元人胡三省在解释《通》东汉章和二年邓训部中的秦胡时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此话大谬,章和二年,此时,建汉已三百年,历十二三代人之久,有什么秦威遗存?钦定的《后汉书》、《通》的著写者,又怎能以夷人口吻写史?秦胡即大秦胡,即古罗马人,实在没丝毫含糊处。
因为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靬人又称作卢水胡。骊靬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延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意即旧时之卢沟。《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靬、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靬戎造反之地。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因为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靬戎。《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靬戎”者虽属绝无仅有之笔。虽少,却实乃为铮铮发光,一字千钧的文字,须引起任何一个史学家的直面。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上确有数以万千计的被称为“秦胡”、“骊靬戎”或“卢水胡”的罗马人在河西生活。尽管他们在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本营却只有一处,即以骊靬县为中心,旁及番和、显美、临松县这一地区,即卢水地区。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第四,河西罗马人来自克拉苏东征军实属必然。西汉时期,中国跟罗马不存在商贸往来。甚至罗马使者也不能通达,自然谈不上罗马商人入汉。原因就是安息阻隔。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的:“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丝绸)与之交市,故庶阂不得自达。”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才有首批大秦使者到中国。那么,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答曰: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为争夺商业和领土,克拉苏发动了对安息的战争。通说克拉苏率五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1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一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14卷)。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 北靠康居, 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来往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响彻昼夜。那些在战场上逃逸的罗马士兵,以及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不堪忍受安息人欺辱的罗马俘虏,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从商道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靬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缘由。
具体完成这一重大行动的人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为陇西狄道人,仕途阅历并不复杂。少时随长罗侯常惠将军屯田乌孙赤城,汉元帝初,举茂材,拜为朝廷郎中车骑将军,寻迁张掖太守,时为初元元年(前48年),八年后迁酒泉太守,因“在两郡著功迹”,成帝初(前32年)征为朝廷光禄大夫,后为光禄勋,元延元年(前12年)去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班固在传中作了这么一段记述:辛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 此处的“西域亲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西域乌孙国时,不过是常惠部下小卒,无关轻重;后为光禄大夫时,管的是顾问应对之事,与西域无关,西域事由典属国掌管。辛庆忌到底是怎么在和平年代而使“匈奴西域亲附”的,答案就在张掖太守中。从时间推算,辛庆忌在张掖、酒泉两郡待了十六年,他在张掖的任期至少是八年,即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0年。《汉书·辛庆忌传》中说他在当车骑将军时“尚未知名”,而迁张掖太守后即“所在著名”,正是他作为朝廷的和平使者,奉命从西域大月氏等地接回要求内迁的罗马流亡军人,安置在他所管辖的番和县南照面山下。以此义举而扬名天下,而成为国家虎臣。从此,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使后人扑朔迷离的县:骊靬县。
第五,居延简的历史回首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有关骊靬的十二枚,尽管纷乱无序,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一惊人的历史现象:
凡是记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记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骊靬县的村庄,又都和番和县无缘,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后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角乐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兒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前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0年以后才出现的。
以西域的地名命名的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内以牧养西域进口的良马为主的国家牧场,地点在番和的城边。人们要问:为什么养马场在公元前50年以后某个时间突然变成县的建制呢?西汉立县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希则旷。” 为什么突然又在“民稀则旷”的番和腹地又另建县城呢?县城又为什么一定要以骊靬二字命名呢?为什么秦胡、卢水胡、骊靬戎偏偏一直居住在此地呢?很明显,建骊靬县,有其因时性,有其特殊性,还有其神秘性。它告诉我们:公元前50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附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谓骊靬人的古罗马人作为一个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靬县并入番和,骊靬存县600余年。
现在,有一个问题使学者们争论不休,即公元前36年,陈汤在对西域郅支匈奴讨伐中所获俘虏里到底有没有罗马流亡军人。这,只要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明白了。根据《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告诉我们的事实:郅支匈奴因屡杀汉使,深怕汉军联合南匈奴消灭他,便合众西迁,至坚昆;时康居国屡为乌孙所困扰,无力自卫。康居国王闻讯郅支西来,派使者至坚昆,答应给郅支在康居东边提供领地,欢迎郅支去驻,目的是将郅支作为屏障以胁乌孙。郅支大悦,移众继续向西。不料中途遇大风雪,数万之众死者十之八九,到康居东,苟活者才三千人,且伤兵者多。三千疲惫之旅,如何抵挡乌孙!郅支向康居王“借兵”,康居王借给郅支了一批人。这就是《陈汤传》中写的“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我们须特别注意“借兵”二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拥有六十万人口之众的康居不能自卫,郅支却靠从康居借来的“这批人”连续大败乌孙,致使乌孙胆寒,不敢西顾;不仅如此,郅支又乘胜骄,靠“这批人”反戈一击,一下子打得康居七零八落。郅支威震西域,成了一霸。“这批人”俨然如同神兵天降。很明显,这是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问题来了:“这批人”在康居那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又向康居反戈一击呢?我们可以断定,“这批人”在康居那里被视为异己,不受重用,为无用之徒,甚至受到歧视;而到郅支这边,疲惫中的匈奴自然要把他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力量。在康居那边他们是寄人篱下的睡狮,在郅支这边他们是腾跃下山的猛虎,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精通战术的战斗部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从安息西部草原上逃跑出来的克拉苏第一军团的部分,几经辗转而投靠康居。他们被借转而成为郅支匈奴的成员,并在后来参与了跟汉军的作战,形成罗马军人跟中国部队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触。首先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中国学者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提了出来。
有人说:“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已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 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克拉苏被重重包围,儿子为护父率军冒死突围在情理之中;克拉苏被俘,儿子为救父战死沙场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军团长战死,必有副军团长继任指挥,副军团长战死,必有另外的副手或下属继任指挥。这也是必然之事。“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显然是一句臆想之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大历史学家阿庇安告诉我们的:罗马军在卡莱战场上突围出了近一万人。为了活下去,这一万人必然要寻机奋力逃出安息,而较为松弛的安息东北边境为他们提供了出界的可能。何况安息首都泰西封就有商贸大道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陈汤俘获的匈奴中确有一批罗马军人。
无可否认,正如《汉书》记载,陈汤所获俘虏全部“赋予城郭诸国”。但《汉书》并未说这批俘虏就全部老死在那里,一直未做任何迁徙。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就可便知,古代环境为一个民族成批迁徙所造成的随意性和频繁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动辄南迁北移是常事。“赋予城郭诸国”的匈奴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断言他们就没有进入玉门关。他们跟骊靬县的建立无关,但却跟骊靬县的县民有缘。公元前48年前后,骊靬已在祁连山下拔地而起。
至于拿出个人对于“重木城”和“鱼鳞阵”的解释为根据,来否定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的部队同汉军作战的历史发现,更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说:“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这是一种臆想妄断。其一,不要忘记,公元64年毁于一场大火的罗马城,房屋基本上是用木料建造的,后建的新城才用石料取而代之,何况筑郅支城是公元前36年前的事,怎么能断然说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其二,倒退一步,就算是罗马军队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但是用兵之道,因势制宜,在彼处修石城者,不能说在此处不能修木城,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态势,罗马人协助郅支单于建造重木城并非天方夜话,惯于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穿起西装打起鲜艳的领带。我们大可不必为罗马人修重木城大惊小怪。
“否定论”者又说:“《陈汤传》中的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这又是一种妄断。他们解释说:“罗马乌龟阵是这样一种阵势。即军队进攻尤其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 这种解释,不攻自破。郅支单于的罗马人出于守城的需要,自然主要将盾牌挡在前面排成鱼鳞阵,演习防守的阵形,不需要“将盾牌高举过顶”的攻城阵形,因为他们眼前的形势是防御。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作战阵形主要承袭古希腊的作战阵形,以战士密集成列的方阵为基本形式,为着作攻防要求可以随时变换其形状。卤盾举过顶形成“乌龟壳”,或者卤盾不举顶而排成鱼鳞状,都是因不同需要而出现的形式变换,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拳击运动员出拳,出左手和出右手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硬要加以区别,而且是本质的只能使自己陷入荒唐。
至此,正如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辞海》在骊靬条目中诠释的那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在今甘肃永昌南。”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罗马城是为古罗马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古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
第一,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中国的一批权威史书,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还指出: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第二,为骊靬降人设县有据可查。《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靬说:“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师古之解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所以如此,就在于它的可靠性。师古也许料到会有人怀疑他的注释,特地向后人交代说:他的注释“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师古语)。其实,早在以前,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这“蛮族”即骊靬人。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诂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涉足骊靬者不乏其人,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靬县取骊靬国名为县名,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中国从汉、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应、颜之说,“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只是由于典籍的大量失传,我们无法看到他们考证时所根据的材料。如徐松、为嘉庆编修,因坐事戍伊犁,致力于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北史地的研究,破疑解难,成绩卓著,为世所公认。现在有人武断地说这些学者结论没有根据,未免过于草率。现在还有人说:颜师古之解始于初唐,跟西汉中期六百多年,不足为凭。如果时间能够成为理由,那么,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距西汉两千多年,距初唐1400多年,更有何资格去评说或否定颜师古搞错了呢?正因为历史遥远,大量资料在不断遗失(这一点只要看看《汉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书目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就是凤毛麟角,如同长夜里的一盏小灯,只能守护,不能把它扑灭。因此,不能否定中国从东汉初唐到清末一批学者对骊靬研究的成果。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若干现代学者在这块土地上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不仅信心十足地坚持了应劭、颜师古之说,而且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前者如向达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后者如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
第三,确有大批古罗马人生活在河西。这批古罗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靬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靬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如《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189年),朝廷徵卓为少府,卓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腹上。”这里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就是湟中羌和大秦胡之意,后面的“羌、胡”就是“湟中义从及秦胡”的概语。秦胡确指古罗马人。有人认为,此处“秦”指汉人,假设如此,那么,下句的“羌、胡敝肠狗态”作何解释?汉人到哪里去了?再如,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曹操施离间计,约韩遂“叙旧”,以引起马超疑心。《魏书》具体记下了会语的情景。《魏书》说:“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防护木栏)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这《魏书》是曹魏朝廷编撰的皇家史,成书早于《三国志》,现在我们无法看到曹魏《魏书》,但这段文字却由南朝的裴松之抄录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注释中,十分可贵。这段文字,“胡”出现两次,前面点出是秦胡,后面就省掉秦字,正好说明“秦”是对该胡属性的限定。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有“属国秦胡卢水”的记载,“秦胡”纯属为民族之称,证据充分。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西汉初个别情况下也确称汉人为秦人,但秦人和秦胡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是两个概念。古史书中将汉人和少数民族并论时,总是讲“华夷”或“夏夷”,从未有过“秦夷”之称。那种把“秦胡”认为是汉、胡之合称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元人胡三省在解释《通》东汉章和二年邓训部中的秦胡时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此话大谬,章和二年,此时,建汉已三百年,历十二三代人之久,有什么秦威遗存?钦定的《后汉书》、《通》的著写者,又怎能以夷人口吻写史?秦胡即大秦胡,即古罗马人,实在没丝毫含糊处。
因为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靬人又称作卢水胡。骊靬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延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意即旧时之卢沟。《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靬、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靬戎造反之地。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因为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靬戎。《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靬戎”者虽属绝无仅有之笔。虽少,却实乃为铮铮发光,一字千钧的文字,须引起任何一个史学家的直面。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上确有数以万千计的被称为“秦胡”、“骊靬戎”或“卢水胡”的罗马人在河西生活。尽管他们在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本营却只有一处,即以骊靬县为中心,旁及番和、显美、临松县这一地区,即卢水地区。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第四,河西罗马人来自克拉苏东征军实属必然。西汉时期,中国跟罗马不存在商贸往来。甚至罗马使者也不能通达,自然谈不上罗马商人入汉。原因就是安息阻隔。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的:“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丝绸)与之交市,故庶阂不得自达。”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才有首批大秦使者到中国。那么,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答曰: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为争夺商业和领土,克拉苏发动了对安息的战争。通说克拉苏率五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1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一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14卷)。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 北靠康居, 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来往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响彻昼夜。那些在战场上逃逸的罗马士兵,以及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不堪忍受安息人欺辱的罗马俘虏,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从商道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靬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缘由。
具体完成这一重大行动的人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为陇西狄道人,仕途阅历并不复杂。少时随长罗侯常惠将军屯田乌孙赤城,汉元帝初,举茂材,拜为朝廷郎中车骑将军,寻迁张掖太守,时为初元元年(前48年),八年后迁酒泉太守,因“在两郡著功迹”,成帝初(前32年)征为朝廷光禄大夫,后为光禄勋,元延元年(前12年)去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班固在传中作了这么一段记述:辛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 此处的“西域亲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西域乌孙国时,不过是常惠部下小卒,无关轻重;后为光禄大夫时,管的是顾问应对之事,与西域无关,西域事由典属国掌管。辛庆忌到底是怎么在和平年代而使“匈奴西域亲附”的,答案就在张掖太守中。从时间推算,辛庆忌在张掖、酒泉两郡待了十六年,他在张掖的任期至少是八年,即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0年。《汉书·辛庆忌传》中说他在当车骑将军时“尚未知名”,而迁张掖太守后即“所在著名”,正是他作为朝廷的和平使者,奉命从西域大月氏等地接回要求内迁的罗马流亡军人,安置在他所管辖的番和县南照面山下。以此义举而扬名天下,而成为国家虎臣。从此,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使后人扑朔迷离的县:骊靬县。
第五,居延简的历史回首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有关骊靬的十二枚,尽管纷乱无序,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一惊人的历史现象:
凡是记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记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骊靬县的村庄,又都和番和县无缘,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后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角乐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兒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前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0年以后才出现的。
以西域的地名命名的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内以牧养西域进口的良马为主的国家牧场,地点在番和的城边。人们要问:为什么养马场在公元前50年以后某个时间突然变成县的建制呢?西汉立县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希则旷。” 为什么突然又在“民稀则旷”的番和腹地又另建县城呢?县城又为什么一定要以骊靬二字命名呢?为什么秦胡、卢水胡、骊靬戎偏偏一直居住在此地呢?很明显,建骊靬县,有其因时性,有其特殊性,还有其神秘性。它告诉我们:公元前50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附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谓骊靬人的古罗马人作为一个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靬县并入番和,骊靬存县600余年。
现在,有一个问题使学者们争论不休,即公元前36年,陈汤在对西域郅支匈奴讨伐中所获俘虏里到底有没有罗马流亡军人。这,只要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明白了。根据《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告诉我们的事实:郅支匈奴因屡杀汉使,深怕汉军联合南匈奴消灭他,便合众西迁,至坚昆;时康居国屡为乌孙所困扰,无力自卫。康居国王闻讯郅支西来,派使者至坚昆,答应给郅支在康居东边提供领地,欢迎郅支去驻,目的是将郅支作为屏障以胁乌孙。郅支大悦,移众继续向西。不料中途遇大风雪,数万之众死者十之八九,到康居东,苟活者才三千人,且伤兵者多。三千疲惫之旅,如何抵挡乌孙!郅支向康居王“借兵”,康居王借给郅支了一批人。这就是《陈汤传》中写的“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我们须特别注意“借兵”二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拥有六十万人口之众的康居不能自卫,郅支却靠从康居借来的“这批人”连续大败乌孙,致使乌孙胆寒,不敢西顾;不仅如此,郅支又乘胜骄,靠“这批人”反戈一击,一下子打得康居七零八落。郅支威震西域,成了一霸。“这批人”俨然如同神兵天降。很明显,这是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问题来了:“这批人”在康居那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又向康居反戈一击呢?我们可以断定,“这批人”在康居那里被视为异己,不受重用,为无用之徒,甚至受到歧视;而到郅支这边,疲惫中的匈奴自然要把他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力量。在康居那边他们是寄人篱下的睡狮,在郅支这边他们是腾跃下山的猛虎,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精通战术的战斗部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从安息西部草原上逃跑出来的克拉苏第一军团的部分,几经辗转而投靠康居。他们被借转而成为郅支匈奴的成员,并在后来参与了跟汉军的作战,形成罗马军人跟中国部队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触。首先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中国学者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提了出来。
有人说:“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已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 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克拉苏被重重包围,儿子为护父率军冒死突围在情理之中;克拉苏被俘,儿子为救父战死沙场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军团长战死,必有副军团长继任指挥,副军团长战死,必有另外的副手或下属继任指挥。这也是必然之事。“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显然是一句臆想之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大历史学家阿庇安告诉我们的:罗马军在卡莱战场上突围出了近一万人。为了活下去,这一万人必然要寻机奋力逃出安息,而较为松弛的安息东北边境为他们提供了出界的可能。何况安息首都泰西封就有商贸大道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陈汤俘获的匈奴中确有一批罗马军人。
无可否认,正如《汉书》记载,陈汤所获俘虏全部“赋予城郭诸国”。但《汉书》并未说这批俘虏就全部老死在那里,一直未做任何迁徙。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就可便知,古代环境为一个民族成批迁徙所造成的随意性和频繁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动辄南迁北移是常事。“赋予城郭诸国”的匈奴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断言他们就没有进入玉门关。他们跟骊靬县的建立无关,但却跟骊靬县的县民有缘。公元前48年前后,骊靬已在祁连山下拔地而起。
至于拿出个人对于“重木城”和“鱼鳞阵”的解释为根据,来否定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的部队同汉军作战的历史发现,更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说:“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这是一种臆想妄断。其一,不要忘记,公元64年毁于一场大火的罗马城,房屋基本上是用木料建造的,后建的新城才用石料取而代之,何况筑郅支城是公元前36年前的事,怎么能断然说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其二,倒退一步,就算是罗马军队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但是用兵之道,因势制宜,在彼处修石城者,不能说在此处不能修木城,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态势,罗马人协助郅支单于建造重木城并非天方夜话,惯于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穿起西装打起鲜艳的领带。我们大可不必为罗马人修重木城大惊小怪。
“否定论”者又说:“《陈汤传》中的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这又是一种妄断。他们解释说:“罗马乌龟阵是这样一种阵势。即军队进攻尤其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 这种解释,不攻自破。郅支单于的罗马人出于守城的需要,自然主要将盾牌挡在前面排成鱼鳞阵,演习防守的阵形,不需要“将盾牌高举过顶”的攻城阵形,因为他们眼前的形势是防御。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作战阵形主要承袭古希腊的作战阵形,以战士密集成列的方阵为基本形式,为着作攻防要求可以随时变换其形状。卤盾举过顶形成“乌龟壳”,或者卤盾不举顶而排成鱼鳞状,都是因不同需要而出现的形式变换,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拳击运动员出拳,出左手和出右手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硬要加以区别,而且是本质的只能使自己陷入荒唐。
至此,正如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辞海》在骊靬条目中诠释的那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在今甘肃永昌南。”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罗马城是为古罗马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古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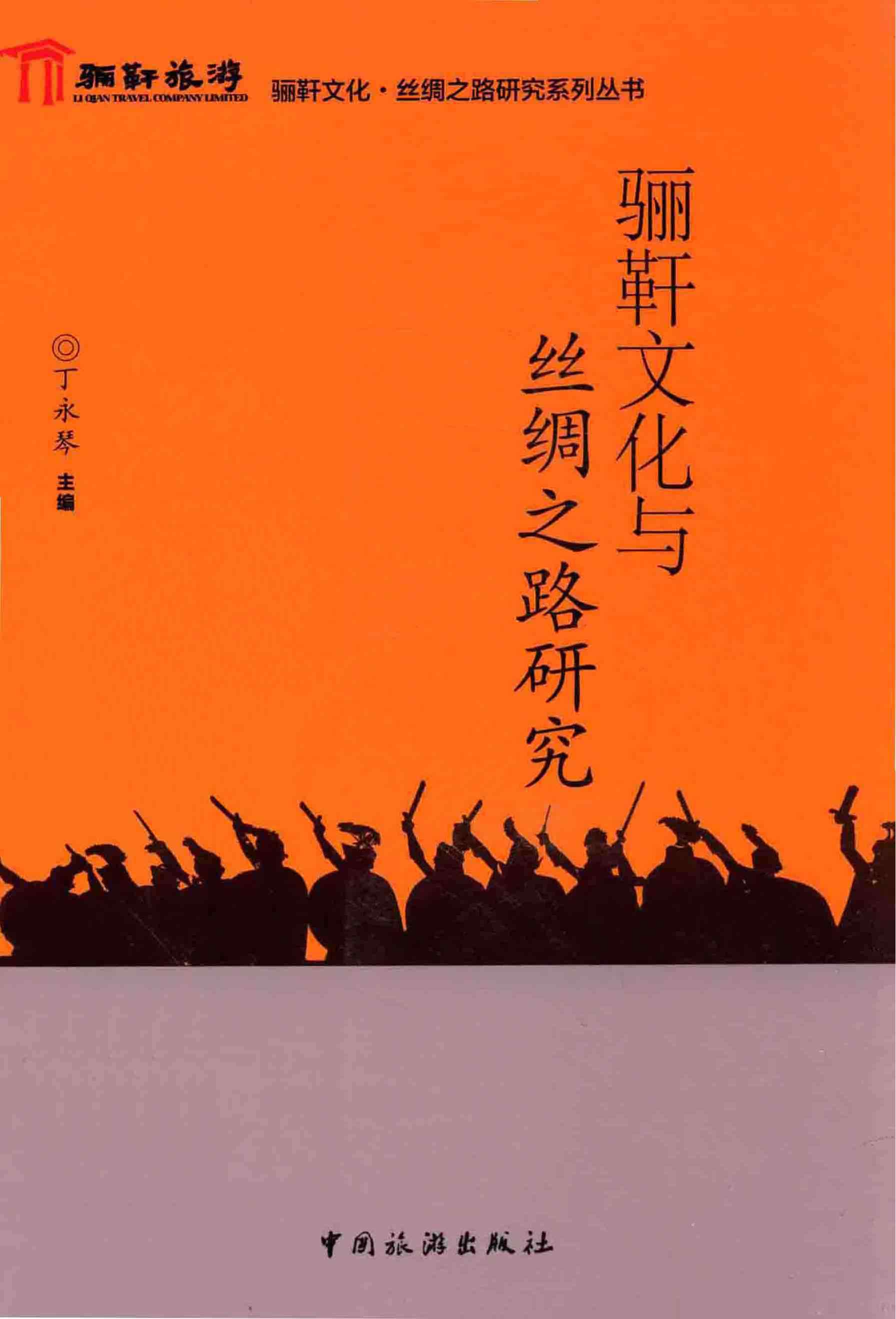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书分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骊靬文化旅游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研究、骊靬文学研究等四部分,收录了《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与战略定位》、《骊靬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展望》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