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鲜说骊靬
| 内容出处: |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33 |
| 颗粒名称: | 王萌鲜说骊靬 |
| 分类号: | K203-53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7-41 |
| 摘要: | 本文是一篇研究骊靬文化及历史研究的文章,此文章是作者于2007年6月根据讲座稿整理而成。 |
| 关键词: | 骊靬文化 文化研究 历史研究 |
内容
一、两个伟大皇帝的憧憬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无独有偶,还有一句,叫相辅相成。小事物是这样,大事物也是这样。公元前1世纪,世界的西方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同一个时间,世界的东方也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西汉王朝。罗马帝国发展到恺撒、庞培、克拉苏“三巨头同盟”时代,已变得空前强大;同时,东方的西汉王朝发展到汉武帝中期,也变得空前强大。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亚、西亚传到了欧洲,也传到了罗马帝国。据罗马史学家卡希攸斯的著作记载,在一次向凯旋的将士授奖时,当恺撒大帝把中国生产的丝绸授给有功的将军的那一刻,几乎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这到底是什么呀?柔软而轻盈,坚韧而新颖,光滑而精致,颜色鲜,光泽斑斓。这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丝绸织品。恺撒说:这些东西来自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国家叫“赛里斯”,即“丝国”的意思。“赛里斯”这个名称也是几经翻译才传到罗马帝国的。老实说,中国的丝绸织品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高科技,犹如20世纪美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罗马皇帝十分神往东方遥远的大帝国,萦绕于心,情难自已,特别想跟这个神秘的东方之“丝国”取得联系。然而,有一个国家首先阻挡他们,这个国家,中国汉代称它为安息,即波斯国,今天的伊朗一带。安息把中国获得的丝绸等高新产品转手卖给古罗马,从中取得高额利润。这使罗马人十分愤怒,于是他们不惜发动战争打通走向中国的道路。古罗马皇帝对中国的相思之情何等深切!
遥远的东方大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传奇式地发展着。安息对罗马冷,对中国却特别热。汉武帝的特别使团到安息国界,安息王派官员及两万骑兵奔波数千里,到东界迎接中国使团,浩浩荡荡,经过数十城才迎接到首都,空前隆重。中国使团返回时,安息派使团一同前来,到中国后,向汉武帝献上大鸟卵和高级魔术师。汉武帝在金碧辉煌的甘泉宫里接见了安息国特使及高级魔术师。一听介绍,才知道高级魔术师的家乡,正是以前张骞提到过的骊靬,即古罗马。魔术师当场向汉武帝表演了口喷火、嘴吞剑的技艺,在这一刻,也使汉武帝和在场的所有中国官员为之目瞪口呆,震惊不已,随后都赞不绝口:神、神、神! 汉武帝向魔术师仔细询问了古罗马的国情及社会风貌。从此,这位中国皇帝对那个遥远的西方大国罗马,梦萦神牵,情有独钟。对待这位罗马魔术师也就特别宠爱和尊重,甚至每次外出巡行时,也一定要带上罗马眩人。这些历史场景,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以生动的笔调做了描述。
真是叫天天应,叫地地灵,中国皇帝和古罗马皇帝的历史情怀,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最初的憧憬结出了友谊之果,谁能想到,汉武帝去世四十年之后,竟然有数千古罗马士兵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中国,中国西北角竟然出现了一个以古罗马国名骊靬二字命名的县份。这个骊靬县的遗址就是今日永昌县的者来寨。
也许有人要问,真的有这个县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
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对骊靬县,中国史书有明确记载。
二、骊靬县,史书记载明确
对骊靬县,史书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或有关地理的篇章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记载。譬如《汉书》说:张掖郡辖县十个,有番和、显美、骊靬、鸾鸟等。这四个县都是永昌古县。当时番和城在今天的焦家庄,显美是今天的清河。有的史书某些文字还表明,骊靬县在番和城附近,靠祁连山。清代康乾时期编成的地理巨著《大清一统志》又十分肯定地指出: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城南者来寨。元代有《大元一统志》,明代有《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大清一统志》是前两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确认骊靬废县在者来寨之见,早于清代。
骊靬县到底建立于西汉何年?没有明确记载。但经过后来特别是现在一些学者的考证认定,它的建立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之间,或者说在公元前45年前后。后面我还要细说。它的撤销时间,史书倒是给予了明确的表述。《隋书》说:开皇中,即592年,隋文帝下令将骊靬并入番和,骊靬以县的建置存在630多年。《晋书》说,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这些文字,不是十分清楚地说明:骊靬县南依南山,北靠番和吗?这样的地方当然就是者来寨了。
那好,既然有这个县,永昌旧县志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某些老祖宗,特别是当时修县志的那些文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县的存在。我们知道,《大清一统志》,乾隆十一年完成的《五凉志》,都明确写了这个县,我们的旧县志乾隆本在编写时参照了《五凉志》,但却删去了骊靬县,为什么?一则,按字义解释,骊靬就是黑色的干牛皮,多可厌! 二则,骊靬又是一个西域番邦之国名,多可怕! 前者和牛联系,我们汉语中有多少美丽动听的词儿,先人偏偏用骊靬二字,后者和番邦联系,他们当然接受不了,删去为好。上世纪40年代,永昌陈世增又写了一个续修本,是手抄本,他明确写进骊靬县,遗址即今者来寨。
骊靬县的存在既已明了,那么,它又是为何而建的呢?这就是我要马上接着说的问题:骊靬探索之旅。
三、骊靬探索之旅
骊靬因何而建?史书正文都没有明确回答。但西汉王朝用这么两个古怪的字来作县名,必有它的深意在里面,不可能是随便而呼的。班固老先生在《汉书》中没有说明,就把难题留给了后人。于是后来的学者就开启了骊靬探索之旅。骊靬探索,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我分别说来。
第一个阶段,是发轫阶段,代表人物为应劭、服虔、颜师古。《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巨著,由于内容翔实,结构严密,文字赡富,很快被世人推崇,但也比较深奥,有许多地方读者弄不明白,于是不少人为之注解。注解者东汉末期最有名最有成就的是应劭和服虔,两人都是博览群书善著文的经学家,所生年代比班固晚七八十年。《后汉书》有他们的传。他们对骊靬县做了解释。应劭在他的《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服虔在注释中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东汉称古罗马帝国为大秦。又过了五百年,唐太宗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颜师古,对《汉书》做了全方位的诠释,他说,他的诠释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后来,也确实被历代推崇为最好的注释本。他解释骊靬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这三位先哲的话,连起来就是:以大秦国国名取名的骊靬县,是为到中国来的一批西域异族而建的。颜师古还特别指出:骊靬,当地居民自呼曰力虔。师古又特别指出,虔字此处读“揭”,就是说,居民自呼曰力揭,自称曰虔(揭)人,这可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实际上已揭开了一个特殊族种的谜底。后面将要细说。
第二个阶段是考证阶段。时间到了清代,大家都知道,满族建立了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界最黑暗残酷的时代。殃及全国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使文人们不敢说话写文章,文人们只好转头去研究古董。这样,事情的另一端出现了好现象:一个空前的考古、考证时期到来了,训古之风大兴,因此清代的古籍考究成绩非凡,为前代所不及。对骊靬的探索也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明确地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宣布:汉代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换句话说,骊靬县为归顺的大秦国人而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惠栋、钱坫、徐松、张澍、王筠、张穆、王先谦等,他们从康熙到光绪几乎囊括整个清代,对骊靬的考证形成了一个研究链。这些人,都是博览群书,学术造诣深,研究态度严谨而名载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像惠栋,是承前启后的大学者;像张穆,后人评价他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学,尤精西北地理文学,对历代各民族交往关系,考证精确,见解独到,极受学界推崇;像徐松,学界认为他对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卓著。这些学者一致认定: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此结论可以说是金声玉振,一字千钧。他们把应劭说的“西域蛮族”身份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了。
第三个阶段是开拓阶段。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新纪元,也为骊靬探索注入活力,注入新的文化元素。骊靬探索中出现了一批崭新的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文化运动,熟谙古今,学贯中西,思维活跃,视野开阔,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于一身,敢于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视自己所占领域的是与非,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发现新的境地,得出更精确的学术结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向达和冯承钧两位先生。
向达,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年至1938年,又到牛津大学、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冯承钧先生幼年出国,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尤精于中西交通史研究。二人都是学术巨擘,史界泰斗。不仅心中铭刻着中华泰山的庄丽,也目睹了欧罗巴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不仅对唐尧虞舜汉武唐宗研究透彻,而且步入希腊罗马殿堂窥其阃奥。因此,他们可以用更新的视角、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骊靬的本源。
向达在自己所著的《中外交通小史》一书中说:“中国史所记述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但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骊靬、大秦、拂森,都是指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向达先生明说了,骊靬县即为归义罗马人而设。冯承钧在他写的《西力东渐记》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匈奴,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罗马人从何而来?冯承钧认为,他们来自入侵波斯的古罗马军团,是失败后的古罗马军团的游勇散兵。这是一个大突破,说明公元前36年,流亡于中亚一带的罗马士兵,他们确系来自卡莱战役失败后的克拉苏的部队。他们徘徊在中国的西大门口。
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谦先生发表了自己的惊世骇俗的长篇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他在研究古罗马战争史的时候十分关注入侵安息失败后罗马大批流亡士兵的下落,终于从《汉书·陈汤传》中发现了他们部分人的身影。他得出了和冯承钧先生同样的结论:一支罗马部队参与了北匈奴郅支单于跟汉军的作战。汉军统帅陈汤把他们俘获后带入关内,在张掖郡设立骊靬县作了安置。德效谦之说,我们可以概括为“陈汤俘获说”。这是骊靬探索的第三阶段,是开拓,是突破,也是中西文化大交融后骊靬探索必然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是张扬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正本清源阶段。骊靬探索在第三阶段后变得悄然无声。时间进入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个年头。和西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空前深入。1989年下半年,《参考消息》及《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的消息,说的是:经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和几位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研究,认为西汉的骊靬县是为安置一批古罗马战俘而设的。他们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府副都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击败北匈奴郅支单于,俘虏了一批罗马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河西走廊,设置县城以领之。这其实是重申了德效谦之说,但在当时经媒体炒作,引起了靬然大波,震动了史学界。本人接着发表出版拙作《骊靬书——支古罗马军团的最后归宿》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尔后,中央电视台介入,《东方时空》、《走近科学》等栏目都多次报道,骊靬的话题推向世界,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但这些宣传和报道,都讲的是“陈汤俘获说”,由于“陈汤俘获说”存在致命的缺陷,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如葛剑雄、刘光华等教授的反驳,反驳的根据也在《汉书·陈汤传》中。因为《陈汤传》讲得十分清楚。书中说此次战役,“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也就是说,陈汤将军把所有的俘虏分赋给了参与汉军作战的十五个在西域的诸侯国,未带一人进关。这种反驳当然也是致命的,将“骊靬县与陈汤有关”的说法彻底击碎,所以“陈汤俘获说”,只能说陈汤的俘虏中有罗马士兵,但与骊靬建县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骊靬探索之旅到此止步了吧?不! 没有止步。“陈汤俘获说”只是探索中的一个分支,探索还正在深入。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常征教授,在1992年第一期的《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以翔实的史料,以严谨的分析,以学者应有的眼光和勇气,探讨了数千罗马兵归顺中国的过程。常征的结论是:古罗马军队在安息失败后,突围的第一军团六千多人辗转到了安息东的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并基本定居下来。公元前40年,大月氏发生“五翕侯”互并的大内战,被排斥的罗马人,越葱岭,傍昆仑山北麓进入河西,归顺汉王朝,另曰“义从胡”,汉王朝为安置他们而设骊靬县。因为他们是由大月氏国归顺的,我们把这一说概括为“月氏归义说”。
另外,不能不特别指出《辞海》关于骊靬的诠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有数百名学者参加,从1958年开始,到1965年完成修订,于1979年再修订后出版的百科综合大辞典《辞海》,在“骊靬”条目下解释道:“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这就是说,骊靬县,为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而建。这一说法,我们称为“骊靬内迁说”。
通过我们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已经明白,对于骊靬何以设县的探索,经过了四个阶段,即起步发轫阶段、深入考证阶段、开拓突破阶段、讨论张扬阶段。时至今日,骊靬何以建县出现了三种说法,即“陈汤俘获说”、“月氏归义说”、“骊靬内迁说”。同时,通过以上回顾,我们还得以明白:首先,对骊靬建县的探索已经过两千年时空,连绵不断,逐步深入,逐步明确,不是某些人说的“子虚乌有”;其次,探索中留下重要论断的人,东汉有应劭,唐代有颜师古,清代有惠栋、顾祖禹、张穆、王先谦等,现代有向达、冯承钧等,他们或者是训诂大师,或者是经学巨儒,或者是史地泰斗,他们一言九鼎之见,光照史册,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空穴来风”;再次,探索者们也许方法不同,叙述有别,但在认知上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骊靬即大秦国,大秦国即古罗马,骊靬建县绝对跟一批骊靬人有关,即跟一批古罗马人有关。汉武帝时期的骊靬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争论。但东汉时期,则认定大秦国即古罗马。《后汉书》说“大秦国一名黎靬”,即骊靬。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三种说法,首肯的当然是“骊靬内迁说”。一则,《辞海》是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的重点项目,是国家科技方面完成的全局意义的系统工程;二则,《辞海》的修订,投入了来自全国各界各领域的学术精英近千人,潜心研究,反复论证,去伪存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三则是它的修订,竟然经过了二十年沧桑岁月的洗练。因此,它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更大的精确性,更广泛的认知性。“骊靬内迁说”,涵盖了清代学者的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建的论断。降人不是指俘虏,而是指归顺、归化、归义、亲附。常征先生的“月氏归义说”和“内迁说”是一致的,不过说得更具体,认为这批骊靬人是从大月氏国越葱岭、沿昆仑山进来的。
四、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
是呀,说法种种,骊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或者说: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这里具体谈谈我的看法。讲四点:一、形势;二、时间;三、路线;四、具体办理人。
(一)形势:我们已经知道,古罗马帝国为打通走进东方的路线发动了对安息的入侵。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七个军团四万多人的部队进攻安息,结果在卡莱遭到安息骑兵的围歼,罗马兵有六千突围,一万被俘。这一万俘虏被送到安息东界守边。近两万罗马士兵稽留在中国西界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安息东界和大月氏接壤。被俘者被当作奴隶看待,不堪忍受虐待而大批逃亡,而沦为难民。突围的罗马兵则成为游荡在中亚盆地的游勇散兵。大月氏既是安息的友谊之邦,也是西汉王朝的友谊之邦。此时,穿过大月氏通向安息的丝绸之路,则显现出“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繁荣景象。汉天子广修文德,恩被天下,让四方来服。条条大路通向长安。西域都护府本身就有接纳归附者的重要任务。大批无家可归的古罗马士兵徘徊在中国西大门,进关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二)时间:指日可待,到底是何日?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德效谦,哈里斯等认定的公元前36年,另一个是常征先生认定的公元前40年,前者,我们前面已经说清,公元前36年陈汤俘获的罗马兵并没入关,已就地分散管之。后者,说的是已定居大月氏的罗马兵因大月氏内乱而逃亡中国,似亦理由不足。按照常理,已经定居,就有了起码的产业,起码的生活资料,不可能轻易离乡背井,弃家而逃。他们进入中国而又被设专县管理,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一是他们必须是流亡者,而不是定居者,只有流荡不定才会寻找栖息地;二是进关以后汉王朝为他们设专县,必须是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人数至少在两三千人以上,否则是不会设县的;三是他们在大月氏、康居等国流亡,时间不能长久,流亡时间过长,人员会自寻着落,队伍就会自行瓦解,也就没有了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卡莱战役是公元前53年,安息西界至东界相距约两千公里,突围的罗马兵团以及被俘的万余人转移至安息以东,需一两年时间;再经逃亡、流动和组合过程,又需一两年时间。这时,一支庞大的难民队伍已经形成。他们是一批职业军人,习惯于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他们与周围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出于生活的需要,必须组织起来;还由于当地居民或许对他们心存戒心甚至敌意,处处设防甚至要消灭他们,为渡过一道道难关,他们必须暂时结成一个群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体弱有病,或者有伤,不能奔波,只好留在当地听天由命了,而由强者结成的难民群体,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极力寻找着落脚安身的地方。因此,我们断定,数千古罗马兵进入中国,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最迟不超过公元前45年。汉骊靬县,就是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设的。
(三)路线:历史事件,总是会在史书中留下蛛丝马迹的。我们读《后汉书·西域传》,会在于阗国中发现一个十分新奇的地名:骊归城。《西域传》文字的叙述十分新奇地告诉我们:骊归城之名得于西汉。为何叫骊归城呢?顾名思义,骊归城就是欢迎骊靬人归顺的城市。可以想见,当年,西汉王朝的使者在这座城市举行了一个大会,欢迎数千骊靬人归顺中国,因为有重要的纪念意义,这座城市即改名为骊归城。丝绸之路南线经过于阗。流亡于西域的数千古罗马人就是从南道经于阗,进入阳关的。骊归城和后来出现在张掖郡的骊靬县形成惊人的呼应。骊归城成了古罗马兵进入中国的历史见证。
(四)具体办理人:班固的《汉书》为一个叫辛庆忌的人立了传。辛庆忌是狄道人,即现在的临洮人。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他就是张掖郡的太守,以后又到酒泉郡当太守。书中说他到张掖前并不知名,但到张掖郡当太守后,一下闻名朝野,成为名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书中这样写道:前在边郡,功劳卓著,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为国之虎臣。“西域亲附”作何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和平年月,辛庆忌完成一桩使西域亲附的大事,再具体说,就是辛庆忌作为汉使,前往于阗迎来一批古罗马人到张掖郡,并为之建县。这样解释有何不可! 因此,我认为骊靬县的具体建置人就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
“先生,你的这种分析有点捕风捉影了吧?”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遗案,有两类:一类证据确凿,另一类证据不全。历史学家为历史事件做出论断,不是为史料充足的事件去做人云亦云的复述或说明,而是为史料欠缺的事件做出合情合理而被后来历史证明正确的判断。正如一个高明医生去解决罕见的疑难杂症一样。要不,我们要历史学家干什么! 捕风捉影,正说明有“风”可捕,有“影”可捉。顺影寻去,影子后面难道不是事物的实体吗?张掖郡出现了一个骊靬县,而汉王朝远在万里之外的属国又有座骊归城,无论如何,不能视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既然有骊靬人归顺,就得给他们一个落脚处;有数千人,就应当建县。
五、虔人、羯、秦胡、卢水胡,原来都是骊靬人之称我们再来察看,骊靬县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中国史书对照面山下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做出了具体而又精彩的描述。骊靬人的生活画卷光彩照人。
《晋书》载:永和十年(354年),凉王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这是史书对骊靬人的最直接的描述。那些反对“骊靬即古罗马,骊靬戎即古罗马人” 之说的先生们,从未直面这段文字,从未做出追根溯源的探讨。
我们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统史书对于古凉州地区特别是河西的少数民族叙述中,总是会碰到这些民族概念:秦胡、卢水胡、力羯、虔人羌、骊靬戎,等等。其实,它们都是骊靬人的称谓。骊靬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东汉时期,中国称古罗马为大秦国,这没有丝毫含糊。因此,骊靬人被称作秦胡,也有时叫卢水胡或虔人。三国时期,骊靬人主要被叫作卢水胡,有时也叫秦胡。两晋及南北朝时期,被称作羯、力羯、骊靬戎等。
这不是胡说,有史为证,让我们一一道来。
先说羯。史书中东汉以前没有羯,东汉开始有了羯,或称羯胡,或称羯人,或称羯族。羯从何来?来自骊靬县。这是唐朝大学者颜师古告诉我们的。师古解释“骊靬”二字的字音时这样说:“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虔”字一字二音,照诚敬的意思读音为“前”,照掠杀的字义读音为“揭”。在这里读“揭”。骊靬,当地人自呼曰“力揭”,当地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我们不妨一试,念得快一些就是“力揭”,再快一些,就成“揭” 了。这样,骊靬县就成了“力揭”,骊靬人就成了“力揭人” “揭人”。怪不得当初王莽改骊靬县为揭虏县。于是“力虔”在演化中成为“羯”、“力羯”、“虔人”等。这些字,都是正统的读书人写的。因为是少数民族,就得写上带“羊”边的羯字了。《后汉书·西羌传》中,多处写到虔人羌,他们与其他羌族联合起来造反。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狼莫羌与虔人羌反,汉军在北地打败他们,“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指虔人羌一万一千人投降了邓遵将军。而《晋书》里对于羯人形象的描述更为具体,说他们“深目、高鼻、多须”(见《石季龙载记》)。“深目高鼻多须”的形状,正是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生理特征,也正是羯人即罗马人的人证。秦胡,即大秦胡的简称,有时叫秦胡,有时也叫大胡。在中国,东汉时期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后汉书》里写到秦胡的篇章有:
其一,东汉章和二年(88年),羌人反。羌豪迷唐率部与武威种羌万余骑,攻至塞下。护羌校尉邓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护迷唐于斜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这里,湟中指小月氏,秦胡即骊靬人。请注意,邓训是在凉州组织了这支军队,里面的秦胡来自凉州地区。(见《后汉书·邓训传》)
其二,同书《段靬传》记载:段靬是武威人也,从小就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好古学。做官就是武将。延熹二年,即公元159年,凉州有八种羌联合起来造反。朝廷任命段靬为护羌校尉,赴凉州去平叛。羌人起势凶猛,相继寇陇西、金城,以及河西四郡。并顽强抵抗汉军。凉州的秦胡骁勇善战。段靬率领以秦胡和湟中月氏为骨干的凉州兵,经十一年的战斗,才将羌叛平息下去。十一年,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建宁三年春,段靬凯旋回京,“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交给朝廷,请注意,武威人段靬部队中的秦胡仍然来自凉州地区。
其三,再看同书《董卓传》。董卓是陇西临洮人。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北地先零羌反,凉州的汉朝官员韩遂、马腾也相继跟着造反。大家知道,马腾是马超的父亲。他们杀了凉州刺史耿鄙,气焰甚盛。朝廷乃任命董卓为破虏前将军,任命一个叫皇甫嵩的官员为破虏左将军。皇甫嵩是凉州安定郡人。二人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平息了先零羌及韩遂、马腾的叛乱。董卓自恃功高,拥兵自重,朝廷调他到京城做大官,但董卓不肯丢掉兵权,借故不去,给皇帝上书说:“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董卓说,他想去,就是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及秦胡把他挡下了,他没办法,只好顺从。请注意,秦胡还是在凉州地区。
其四,我们再看《三国志》,在《武帝纪》中也具体写了秦胡。建安十六年(201年),西凉的马超与韩遂起兵反叛,洛阳大恐。马超离他老子的反叛隔了二十七年。老子的对手是董卓、皇甫嵩,马超的对手是曹操。曹操与之交战,开始屡屡受挫。
曹操说:“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他决定智取,施离间计。韩遂与曹操是老熟人,曹操要求和韩遂说几句话,于是在两军前,与韩遂寒暄片刻。后日,又相见。《三国志·注解》引用了《魏书》对这次相见的具体描绘:
“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惧。”
“可为木行马”,是说在前面架起粗木防护栏。这段文字,可以说写得绘形绘神,十分精彩。曹操的这一招也真灵,和韩遂说的不过几句随便的叙旧话,但引起马超怀疑,结果马、韩自相火并,导致失败。请注意,这些秦胡兵还是来自西凉。
上述文字,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写秦胡的仅有的篇章,也是所有史书具体写到秦胡的仅有的篇章。这些篇章明确告诉我们:秦胡就生活在西凉地区,是西凉生活的一个少数民族。这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秦胡到底生活在凉州的哪个地方呢?这里,就不能不讲到有名的卢水胡。说实话,对“秦胡”的概念,曾经有史学家做过另外的解释,但我们上面所举史实表明,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民族概念,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称呼。1976年,在张掖北部的汉居延遗址,发现两万多枚竹、木汉简,其中一枚上有六字“属国秦胡卢水”。属国指张掖属国。这句话说清楚,就是:张掖属国卢水地区的秦胡。秦胡生活在卢水地区。这汉简就是铁证。
而卢水地区又指哪一带呢?让我们走进《后汉书》和《三国志》所描绘的世界,里面的卢水胡会告诉我们:卢水就在骊靬县。不信请看:
其一,《后汉书·西羌传》说,建初二年(77年)夏,迷吾羌聚众反,“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说的是张掖属国管辖的卢水胡。很显然,卢水胡在张掖郡。
其二,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4年),汉明帝为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发七万兵力,从玉门关到雁门关这一条线上,分四路进击西域。《窦固传》中是这样写河西这一路的:“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胡,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很显然,这里说的卢水胡仍然在张掖郡。
其三,同书《邓训传》中说:“元和三年(86年),卢水胡反叛,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东汉光武时,武威郡治从民勤北迁到了姑臧。邓训是受命去平息卢水胡的。任务艰巨,情势紧迫,需快马加鞭火速投入工作。但这里,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乘驿车去上任的邓训,本应到张掖郡去当太守,怎么待在武威郡当起了张掖太守?其中究竟有何玄机?答案很明白,也很简单。因为出了武威西门,就是卢水胡的天下。姑臧以西是什么地方?是显美、骊靬、番和。反叛的卢水胡就聚集在骊靬一带,邓训只能在武威,实施他的平叛计划。很显然,卢水胡就居住在张掖郡的骊靬县一带地区,延及番和、显美。
其四,再看《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刚当上皇帝,卢水胡在伊健妓妾、治元多、封赏等人的领导下起兵造反,武威、张掖、酒泉的太守也率郡相应,河西形成割据之势。实际上这是河西人反对曹魏朝廷的政治起义。曹丕派镇西将军曹真率十万大军来镇压,又任命文武全才张既为凉州刺史,辅曹真军事。《三国志》对这次战争作了十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简要概括一下曹真、张既取胜的经过:(1)渡黄河从景泰直插武威、攻下武威,切断已攻到永登的卢水胡先锋后路;(2)诱敌深入,前后夹击,歼灭显美的卢水胡,俘虏万余人;(3)派新任的武威太守贯丘兴深入卢水胡大本营骊靬番和,说服卢水胡放下武器。书中写:“兴(贯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皆弃恶诣兴,兴皆安恤。”(4)安抚卢水胡后,迫使叛官张掖太守张进、酒泉太守黄华投降,河西遂平。此次平叛,历时二年,斩首五万余级,俘虏十万余,可见规模之大。请注意,《三国志》中这些文字,具体准确地告诉我们:卢水胡生活的大本营就是骊靬县,旁及番和、显美的一些地方。反叛队伍里当然也有不少汉民,但起事者头头是卢水胡人,书中只能概称为卢水胡。
其实,卢水就是今日的者来河。永昌地名普查时发现,当地老人仍把者来河上游叫早卢沟,即当年卢水河之意也。这就是明证:卢水就是者来河,它穿过番和,流入金川河。这就是卢水地区,万千异族生活在这里,按民族性讲,他们叫秦胡,按生活地域讲,他们叫卢水胡。汉简“属国秦胡卢水”,明确记载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自己疾呼曰力揭,王莽称他们为揭虏,提法又演化成羯人。
另外,《后汉书》还有两处提到卢水胡,一处是《西羌传》中,说:中平二年,烧何羌犯卢水胡,为卢水胡所重创,头人比铜钳率众去依附临羌县。临羌在今西宁附近。按此情判断,卢水胡重创比铜钳的地方,应该是骊靬县南山的北麓。再一处是《西南夷传》里提到的一句:“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黄石旧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北地即今宁夏吴忠市一带。这两地的卢水胡,是从河西东迁过去的骊靬人,缘由在后面细说。
在上面,我已向大家提供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具体写到卢水胡的全部文献史料,是忠实、直接地提供,没有断章取义,也没移花接木。之前的史籍中没有这个民族概念,以后,也只是在《魏书》中提到:北魏太平真君六年,一个叫盖吴的卢水胡人,在陕西杏城领导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自称天台王,最后失败。我想,任何人只要他忠实于那些历史文字的叙述内容,都不会作出另外的判断。
晋代,骊靬人在武威郡叫骊靬戎,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晋书·张祚传》中的有关记载。该传说:永和十年(354年),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晋代,骊靬县属武威郡。张祚在武威自立凉王,骊靬戎不服,揭竿起义,并打败了前来讨伐的和昊将军的部队。公元22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是卢水胡,时间过去13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又是骊靬戎,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恰好说明,卢水胡本身就是骊靬人。
好了,我们以时间先后做排列,做个小结看看骊靬县居民称呼的演变情况:
公元前48年一前45年,骊靬建县;对骊靬,当地居民疾言之曰:力(虔)揭,自呼曰:力揭人;公元8年,王莽改制,称骊靬为揭虏;公元88年,邓训在西凉发湟中月氏、秦胡、羌兵四千,出击迷唐;公元201年,马超率西凉秦胡反;公元74年,窦固率张掖属国卢水胡出征西域;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公元221年,武威太守贯丘兴到骊靬县和卢水胡谈判;公元354年,骊靬县的骊靬戎打败张祚的讨伐部队。结论:在中国的古罗马人叫骊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又被称之为揭虏、力羯、羯人、虔人、秦胡、大胡、卢水胡、骊靬戎等。
至此,我们不能不请出两位骊靬人皇帝和大家见面。他俩是谁呢?他俩,一个就是羯人石勒,另一个就是卢水胡沮渠蒙逊。前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赵,后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北凉。
石勒,山西上党武乡羯人,即骊靬人,字世龙,又名匐勒。有勇略、善骑射、自幼常代父亲掌管部落事务,为众所服。西晋太安中被晋军掠卖山东为奴,与一个叫汲桑的人聚众起义,一度攻取邺城,后兵败,投汉国刘渊为将,作战有勇有谋,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权位日重。大兴二年(319年)自建政权,号称赵王,史称后赵。据有冀、并、幽州及辽西一带。公元330年称帝,改元建平。在位期间,删减律令,立朝仪核户籍,定祖赋,兴学校,于诸郡立学官,办了不少好事。
沮渠蒙逊,张掖郡临松卢水胡人,也即骊靬人。其祖先曾在匈奴做过官。沮渠蒙逊初为后凉吕光部下。《晋书》说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才有英略,滑稽善权变,甚为吕光所器重。公元397年,叛吕光自立政权,史称北凉,据张掖,自称张掖公,改元永安。永安十二年,迁都武威,改称河西王。寻继灭西凉,占有西凉七郡,界连西域,在位32年。
六、古罗马人过黄河
既然卢水胡的家乡是骊靬,卢水是骊靬、番和一带,为什么黄河以东也出现了卢水胡,如北地卢水胡、杏城卢水胡?山西出现了羯人?道理很简单,河西骊靬人即中国的罗马人,到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发生过几次东迁的事,这是因为发生几次重大军事行动,简而言之,主要是:第一次,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西征魏嚣,时为河西大将军的窦融,率河西数万汉、胡步骑,以及辎重五千余辆,过黄河拜光武于高平(今固原),联合击败魏嚣,并将军队交给光武帝。窦融被封为安丰侯。这批投入光武帝统一大业的河西兵(自然有不少秦胡),战争结束后被安置于河东。
第二次,窦固征西域,率张掖甲卒及卢水胡出酒泉塞,战争结束后,部分被带回洛阳。
第三次,建宁三年春(170年),段靬率西凉五万秦胡步骑及汗血千里马回洛阳。
第四次,董卓讨平羌叛之后,被认命为并州刺史,他不放兵权,并把这支有骊靬人在内的西凉兵带到了山西,后被召入京,他又把部分西凉兵带入京城。
第五次,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韩遂反叛,带领以秦胡为骨干的西凉兵与曹操大战于潼关,最后曹操击败马、韩,并将俘获的西凉兵编入自己的部队。
第六次,三国黄初元年至三年,骊靬卢水胡反叛,镇西将军曹真率大军西征卢水胡,最后卢水胡败,曹真带十万俘虏回洛阳。
这六次,都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这些随军而东的西凉兵,年高退役后,基本就地安置,在那里繁衍生息,于是那里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即羯胡、卢水胡。
七、金关汉简告诉给我们什么
汉代有名的居延海在张掖以北,现在这里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汉代,这里是重要的边防关塞。1972—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两万多枚汉简。简册内容广泛,涉及汉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以屯戍内容为多,且保存了一部分汉代官方文献。这批简,又被称为居延金关汉简。已确定,它们在被埋时已经十分散乱,出土以后,年代及内容也颇多错乱。《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4版,公布了汉简中涉及骊靬内容的13枚,到底如何解读,还需要商榷。这13枚简,现全部抄录如下: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
简三:“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
简四:“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
简五:“□出钱五十,栗五斗,骊靬。”
简六:“靬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
简七:“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
简八:“出栗二斗四升,以食骊靬单门安。” 简九:“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
简十:“□过所遣骊靬禀尉刘步贤□。”
简十一:“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
简十二:“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
简十三:“骊靬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上列汉简,乍一看来,确实有点叫人眼花缭乱。有人看到简一中“神爵二年三月”六字,便啧啧说道:“骊靬建县与古罗马人无关,因为神爵二年已经有了骊靬县,神爵二年是公元前60年,古罗马人侵安息的卡莱战役发生在公元前53年。”
但是,请看清楚一点,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简文,毋庸置疑地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苑、县有天壤之别,前者是马场,后者是行政建制,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人一生的照片,放得无论怎样错乱,仍然能够从体貌上分辨出时间段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分辨出上列汉简的时间段。
如果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惊人的现象:它们清楚地分为骊靬苑、骊靬县两大类,凡是记录苑的,都牵连着番和县,凡是记录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苑内的工作人员,必然来自番和县,凡在县衙服差的,都和番和县无关;凡涉及苑的村庄,都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涉及骊靬县的村庄,也都和番和县无关。对苑、县的记录是如此泾渭分明。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清楚:苑跟番和脱离不了联系,是因为苑本身就设在番和县境内,所以勤杂人员必然也只能来自周围的番和县村庄,作为马场的骊靬苑不可能有自己的行政村;骊靬县跟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骊靬苑已从番和境内分割出来,以县份的面目出现,有了骊靬县自己的行政村,所以其当差人员不是来自番和而是来自骊靬本县。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无须假设,也无须估算,和骊靬有关的13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清晰地呈现出它们的真面貌。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属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简一、简二、简十一、简十二、简十三五枚,为一大类,属于骊靬苑时期的文书内容;简四等另外八枚,为另一大类,属于骊靬县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时间在前,骊靬县时间在后。前者表明,骊靬苑设在番和境内,故啬夫、杂役、牧奴等固然都来自番和,负责人为苑监;后者表明,从番和分割出来的骊靬县,以行政建制独立存在,人员再不需要从番和招募,自然要从骊靬本县的行政村招募来。负责人为县长。
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纪年简面目也清楚了,神爵二年为公元前60年,它明确告诉我们,此时只有骊靬苑,没有骊靬县,此简是骊靬苑时期的。换句话说,它明确告诉我们:公元前59年之前没有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的某年,骊靬神秘地以行政县的面目出现了。
西汉王朝为抵御外侮,在西北边郡建立养育军马的牧苑三十六所。祁连山下,番和之地,有丰富的草场,在番和境内建立马场,合情合理。之所以将番和的马场取名为骊靬苑,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之处。一则,骊本义就是黑马;二则,也许专门养育的是来自西域的胡马,故名;三则,也许体现西汉皇帝对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番邦的向往,故名。但问题是:为什么骊靬苑突然变成了县?为什么建县以后仍然坚持这个对人不尊的名字呢?而且,《汉书》告诉我们:西汉建县有一条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还为什么从民稀的番和县内切割出蕞尔之地另建起一个县呢?显然,其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不建置骊靬县,就不能最妥当地处理当时的特别事件,究竟是何特殊事件?这就是公元前48年至前45年之间,数千流亡在中国西界之外的古罗马士兵归顺西汉,他们正好来自遥远的骊靬国,番和县正好有个骊靬苑,这里过去是折兰王府,现在又是牧苑,设置条件具备,所以正好可以把这批人安置在这里,建县以领之,名字也无须改了。这不是“说曹操曹操到”,太有点巧合了吧?其实,无巧不成书,整个历史就是由无数巧合构成的。偶然构成必然。历史上“说曹操,曹操到”的事件还少吗?正是番和境内有个骊靬苑,后来归顺的骊靬人被安置在番和境内另建县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作者于2006年4月14日下午金昌市党校小礼堂做讲座。此稿是作者于2007年6月根据讲座稿整理而成。)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无独有偶,还有一句,叫相辅相成。小事物是这样,大事物也是这样。公元前1世纪,世界的西方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同一个时间,世界的东方也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西汉王朝。罗马帝国发展到恺撒、庞培、克拉苏“三巨头同盟”时代,已变得空前强大;同时,东方的西汉王朝发展到汉武帝中期,也变得空前强大。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亚、西亚传到了欧洲,也传到了罗马帝国。据罗马史学家卡希攸斯的著作记载,在一次向凯旋的将士授奖时,当恺撒大帝把中国生产的丝绸授给有功的将军的那一刻,几乎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这到底是什么呀?柔软而轻盈,坚韧而新颖,光滑而精致,颜色鲜,光泽斑斓。这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丝绸织品。恺撒说:这些东西来自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国家叫“赛里斯”,即“丝国”的意思。“赛里斯”这个名称也是几经翻译才传到罗马帝国的。老实说,中国的丝绸织品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高科技,犹如20世纪美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罗马皇帝十分神往东方遥远的大帝国,萦绕于心,情难自已,特别想跟这个神秘的东方之“丝国”取得联系。然而,有一个国家首先阻挡他们,这个国家,中国汉代称它为安息,即波斯国,今天的伊朗一带。安息把中国获得的丝绸等高新产品转手卖给古罗马,从中取得高额利润。这使罗马人十分愤怒,于是他们不惜发动战争打通走向中国的道路。古罗马皇帝对中国的相思之情何等深切!
遥远的东方大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传奇式地发展着。安息对罗马冷,对中国却特别热。汉武帝的特别使团到安息国界,安息王派官员及两万骑兵奔波数千里,到东界迎接中国使团,浩浩荡荡,经过数十城才迎接到首都,空前隆重。中国使团返回时,安息派使团一同前来,到中国后,向汉武帝献上大鸟卵和高级魔术师。汉武帝在金碧辉煌的甘泉宫里接见了安息国特使及高级魔术师。一听介绍,才知道高级魔术师的家乡,正是以前张骞提到过的骊靬,即古罗马。魔术师当场向汉武帝表演了口喷火、嘴吞剑的技艺,在这一刻,也使汉武帝和在场的所有中国官员为之目瞪口呆,震惊不已,随后都赞不绝口:神、神、神! 汉武帝向魔术师仔细询问了古罗马的国情及社会风貌。从此,这位中国皇帝对那个遥远的西方大国罗马,梦萦神牵,情有独钟。对待这位罗马魔术师也就特别宠爱和尊重,甚至每次外出巡行时,也一定要带上罗马眩人。这些历史场景,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以生动的笔调做了描述。
真是叫天天应,叫地地灵,中国皇帝和古罗马皇帝的历史情怀,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最初的憧憬结出了友谊之果,谁能想到,汉武帝去世四十年之后,竟然有数千古罗马士兵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中国,中国西北角竟然出现了一个以古罗马国名骊靬二字命名的县份。这个骊靬县的遗址就是今日永昌县的者来寨。
也许有人要问,真的有这个县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
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对骊靬县,中国史书有明确记载。
二、骊靬县,史书记载明确
对骊靬县,史书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或有关地理的篇章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记载。譬如《汉书》说:张掖郡辖县十个,有番和、显美、骊靬、鸾鸟等。这四个县都是永昌古县。当时番和城在今天的焦家庄,显美是今天的清河。有的史书某些文字还表明,骊靬县在番和城附近,靠祁连山。清代康乾时期编成的地理巨著《大清一统志》又十分肯定地指出: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城南者来寨。元代有《大元一统志》,明代有《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大清一统志》是前两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确认骊靬废县在者来寨之见,早于清代。
骊靬县到底建立于西汉何年?没有明确记载。但经过后来特别是现在一些学者的考证认定,它的建立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之间,或者说在公元前45年前后。后面我还要细说。它的撤销时间,史书倒是给予了明确的表述。《隋书》说:开皇中,即592年,隋文帝下令将骊靬并入番和,骊靬以县的建置存在630多年。《晋书》说,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这些文字,不是十分清楚地说明:骊靬县南依南山,北靠番和吗?这样的地方当然就是者来寨了。
那好,既然有这个县,永昌旧县志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某些老祖宗,特别是当时修县志的那些文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县的存在。我们知道,《大清一统志》,乾隆十一年完成的《五凉志》,都明确写了这个县,我们的旧县志乾隆本在编写时参照了《五凉志》,但却删去了骊靬县,为什么?一则,按字义解释,骊靬就是黑色的干牛皮,多可厌! 二则,骊靬又是一个西域番邦之国名,多可怕! 前者和牛联系,我们汉语中有多少美丽动听的词儿,先人偏偏用骊靬二字,后者和番邦联系,他们当然接受不了,删去为好。上世纪40年代,永昌陈世增又写了一个续修本,是手抄本,他明确写进骊靬县,遗址即今者来寨。
骊靬县的存在既已明了,那么,它又是为何而建的呢?这就是我要马上接着说的问题:骊靬探索之旅。
三、骊靬探索之旅
骊靬因何而建?史书正文都没有明确回答。但西汉王朝用这么两个古怪的字来作县名,必有它的深意在里面,不可能是随便而呼的。班固老先生在《汉书》中没有说明,就把难题留给了后人。于是后来的学者就开启了骊靬探索之旅。骊靬探索,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我分别说来。
第一个阶段,是发轫阶段,代表人物为应劭、服虔、颜师古。《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巨著,由于内容翔实,结构严密,文字赡富,很快被世人推崇,但也比较深奥,有许多地方读者弄不明白,于是不少人为之注解。注解者东汉末期最有名最有成就的是应劭和服虔,两人都是博览群书善著文的经学家,所生年代比班固晚七八十年。《后汉书》有他们的传。他们对骊靬县做了解释。应劭在他的《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服虔在注释中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东汉称古罗马帝国为大秦。又过了五百年,唐太宗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颜师古,对《汉书》做了全方位的诠释,他说,他的诠释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后来,也确实被历代推崇为最好的注释本。他解释骊靬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这三位先哲的话,连起来就是:以大秦国国名取名的骊靬县,是为到中国来的一批西域异族而建的。颜师古还特别指出:骊靬,当地居民自呼曰力虔。师古又特别指出,虔字此处读“揭”,就是说,居民自呼曰力揭,自称曰虔(揭)人,这可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实际上已揭开了一个特殊族种的谜底。后面将要细说。
第二个阶段是考证阶段。时间到了清代,大家都知道,满族建立了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界最黑暗残酷的时代。殃及全国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使文人们不敢说话写文章,文人们只好转头去研究古董。这样,事情的另一端出现了好现象:一个空前的考古、考证时期到来了,训古之风大兴,因此清代的古籍考究成绩非凡,为前代所不及。对骊靬的探索也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明确地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宣布:汉代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换句话说,骊靬县为归顺的大秦国人而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惠栋、钱坫、徐松、张澍、王筠、张穆、王先谦等,他们从康熙到光绪几乎囊括整个清代,对骊靬的考证形成了一个研究链。这些人,都是博览群书,学术造诣深,研究态度严谨而名载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像惠栋,是承前启后的大学者;像张穆,后人评价他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学,尤精西北地理文学,对历代各民族交往关系,考证精确,见解独到,极受学界推崇;像徐松,学界认为他对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卓著。这些学者一致认定: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此结论可以说是金声玉振,一字千钧。他们把应劭说的“西域蛮族”身份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了。
第三个阶段是开拓阶段。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新纪元,也为骊靬探索注入活力,注入新的文化元素。骊靬探索中出现了一批崭新的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文化运动,熟谙古今,学贯中西,思维活跃,视野开阔,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于一身,敢于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视自己所占领域的是与非,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发现新的境地,得出更精确的学术结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向达和冯承钧两位先生。
向达,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年至1938年,又到牛津大学、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冯承钧先生幼年出国,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尤精于中西交通史研究。二人都是学术巨擘,史界泰斗。不仅心中铭刻着中华泰山的庄丽,也目睹了欧罗巴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不仅对唐尧虞舜汉武唐宗研究透彻,而且步入希腊罗马殿堂窥其阃奥。因此,他们可以用更新的视角、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骊靬的本源。
向达在自己所著的《中外交通小史》一书中说:“中国史所记述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但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骊靬、大秦、拂森,都是指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向达先生明说了,骊靬县即为归义罗马人而设。冯承钧在他写的《西力东渐记》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匈奴,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罗马人从何而来?冯承钧认为,他们来自入侵波斯的古罗马军团,是失败后的古罗马军团的游勇散兵。这是一个大突破,说明公元前36年,流亡于中亚一带的罗马士兵,他们确系来自卡莱战役失败后的克拉苏的部队。他们徘徊在中国的西大门口。
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谦先生发表了自己的惊世骇俗的长篇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他在研究古罗马战争史的时候十分关注入侵安息失败后罗马大批流亡士兵的下落,终于从《汉书·陈汤传》中发现了他们部分人的身影。他得出了和冯承钧先生同样的结论:一支罗马部队参与了北匈奴郅支单于跟汉军的作战。汉军统帅陈汤把他们俘获后带入关内,在张掖郡设立骊靬县作了安置。德效谦之说,我们可以概括为“陈汤俘获说”。这是骊靬探索的第三阶段,是开拓,是突破,也是中西文化大交融后骊靬探索必然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是张扬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正本清源阶段。骊靬探索在第三阶段后变得悄然无声。时间进入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个年头。和西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空前深入。1989年下半年,《参考消息》及《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的消息,说的是:经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和几位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研究,认为西汉的骊靬县是为安置一批古罗马战俘而设的。他们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府副都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击败北匈奴郅支单于,俘虏了一批罗马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河西走廊,设置县城以领之。这其实是重申了德效谦之说,但在当时经媒体炒作,引起了靬然大波,震动了史学界。本人接着发表出版拙作《骊靬书——支古罗马军团的最后归宿》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尔后,中央电视台介入,《东方时空》、《走近科学》等栏目都多次报道,骊靬的话题推向世界,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但这些宣传和报道,都讲的是“陈汤俘获说”,由于“陈汤俘获说”存在致命的缺陷,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如葛剑雄、刘光华等教授的反驳,反驳的根据也在《汉书·陈汤传》中。因为《陈汤传》讲得十分清楚。书中说此次战役,“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也就是说,陈汤将军把所有的俘虏分赋给了参与汉军作战的十五个在西域的诸侯国,未带一人进关。这种反驳当然也是致命的,将“骊靬县与陈汤有关”的说法彻底击碎,所以“陈汤俘获说”,只能说陈汤的俘虏中有罗马士兵,但与骊靬建县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骊靬探索之旅到此止步了吧?不! 没有止步。“陈汤俘获说”只是探索中的一个分支,探索还正在深入。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常征教授,在1992年第一期的《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以翔实的史料,以严谨的分析,以学者应有的眼光和勇气,探讨了数千罗马兵归顺中国的过程。常征的结论是:古罗马军队在安息失败后,突围的第一军团六千多人辗转到了安息东的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并基本定居下来。公元前40年,大月氏发生“五翕侯”互并的大内战,被排斥的罗马人,越葱岭,傍昆仑山北麓进入河西,归顺汉王朝,另曰“义从胡”,汉王朝为安置他们而设骊靬县。因为他们是由大月氏国归顺的,我们把这一说概括为“月氏归义说”。
另外,不能不特别指出《辞海》关于骊靬的诠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有数百名学者参加,从1958年开始,到1965年完成修订,于1979年再修订后出版的百科综合大辞典《辞海》,在“骊靬”条目下解释道:“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这就是说,骊靬县,为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而建。这一说法,我们称为“骊靬内迁说”。
通过我们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已经明白,对于骊靬何以设县的探索,经过了四个阶段,即起步发轫阶段、深入考证阶段、开拓突破阶段、讨论张扬阶段。时至今日,骊靬何以建县出现了三种说法,即“陈汤俘获说”、“月氏归义说”、“骊靬内迁说”。同时,通过以上回顾,我们还得以明白:首先,对骊靬建县的探索已经过两千年时空,连绵不断,逐步深入,逐步明确,不是某些人说的“子虚乌有”;其次,探索中留下重要论断的人,东汉有应劭,唐代有颜师古,清代有惠栋、顾祖禹、张穆、王先谦等,现代有向达、冯承钧等,他们或者是训诂大师,或者是经学巨儒,或者是史地泰斗,他们一言九鼎之见,光照史册,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空穴来风”;再次,探索者们也许方法不同,叙述有别,但在认知上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骊靬即大秦国,大秦国即古罗马,骊靬建县绝对跟一批骊靬人有关,即跟一批古罗马人有关。汉武帝时期的骊靬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争论。但东汉时期,则认定大秦国即古罗马。《后汉书》说“大秦国一名黎靬”,即骊靬。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三种说法,首肯的当然是“骊靬内迁说”。一则,《辞海》是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的重点项目,是国家科技方面完成的全局意义的系统工程;二则,《辞海》的修订,投入了来自全国各界各领域的学术精英近千人,潜心研究,反复论证,去伪存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三则是它的修订,竟然经过了二十年沧桑岁月的洗练。因此,它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更大的精确性,更广泛的认知性。“骊靬内迁说”,涵盖了清代学者的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建的论断。降人不是指俘虏,而是指归顺、归化、归义、亲附。常征先生的“月氏归义说”和“内迁说”是一致的,不过说得更具体,认为这批骊靬人是从大月氏国越葱岭、沿昆仑山进来的。
四、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
是呀,说法种种,骊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或者说: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这里具体谈谈我的看法。讲四点:一、形势;二、时间;三、路线;四、具体办理人。
(一)形势:我们已经知道,古罗马帝国为打通走进东方的路线发动了对安息的入侵。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七个军团四万多人的部队进攻安息,结果在卡莱遭到安息骑兵的围歼,罗马兵有六千突围,一万被俘。这一万俘虏被送到安息东界守边。近两万罗马士兵稽留在中国西界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安息东界和大月氏接壤。被俘者被当作奴隶看待,不堪忍受虐待而大批逃亡,而沦为难民。突围的罗马兵则成为游荡在中亚盆地的游勇散兵。大月氏既是安息的友谊之邦,也是西汉王朝的友谊之邦。此时,穿过大月氏通向安息的丝绸之路,则显现出“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繁荣景象。汉天子广修文德,恩被天下,让四方来服。条条大路通向长安。西域都护府本身就有接纳归附者的重要任务。大批无家可归的古罗马士兵徘徊在中国西大门,进关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二)时间:指日可待,到底是何日?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德效谦,哈里斯等认定的公元前36年,另一个是常征先生认定的公元前40年,前者,我们前面已经说清,公元前36年陈汤俘获的罗马兵并没入关,已就地分散管之。后者,说的是已定居大月氏的罗马兵因大月氏内乱而逃亡中国,似亦理由不足。按照常理,已经定居,就有了起码的产业,起码的生活资料,不可能轻易离乡背井,弃家而逃。他们进入中国而又被设专县管理,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一是他们必须是流亡者,而不是定居者,只有流荡不定才会寻找栖息地;二是进关以后汉王朝为他们设专县,必须是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人数至少在两三千人以上,否则是不会设县的;三是他们在大月氏、康居等国流亡,时间不能长久,流亡时间过长,人员会自寻着落,队伍就会自行瓦解,也就没有了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卡莱战役是公元前53年,安息西界至东界相距约两千公里,突围的罗马兵团以及被俘的万余人转移至安息以东,需一两年时间;再经逃亡、流动和组合过程,又需一两年时间。这时,一支庞大的难民队伍已经形成。他们是一批职业军人,习惯于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他们与周围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出于生活的需要,必须组织起来;还由于当地居民或许对他们心存戒心甚至敌意,处处设防甚至要消灭他们,为渡过一道道难关,他们必须暂时结成一个群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体弱有病,或者有伤,不能奔波,只好留在当地听天由命了,而由强者结成的难民群体,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极力寻找着落脚安身的地方。因此,我们断定,数千古罗马兵进入中国,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最迟不超过公元前45年。汉骊靬县,就是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设的。
(三)路线:历史事件,总是会在史书中留下蛛丝马迹的。我们读《后汉书·西域传》,会在于阗国中发现一个十分新奇的地名:骊归城。《西域传》文字的叙述十分新奇地告诉我们:骊归城之名得于西汉。为何叫骊归城呢?顾名思义,骊归城就是欢迎骊靬人归顺的城市。可以想见,当年,西汉王朝的使者在这座城市举行了一个大会,欢迎数千骊靬人归顺中国,因为有重要的纪念意义,这座城市即改名为骊归城。丝绸之路南线经过于阗。流亡于西域的数千古罗马人就是从南道经于阗,进入阳关的。骊归城和后来出现在张掖郡的骊靬县形成惊人的呼应。骊归城成了古罗马兵进入中国的历史见证。
(四)具体办理人:班固的《汉书》为一个叫辛庆忌的人立了传。辛庆忌是狄道人,即现在的临洮人。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他就是张掖郡的太守,以后又到酒泉郡当太守。书中说他到张掖前并不知名,但到张掖郡当太守后,一下闻名朝野,成为名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书中这样写道:前在边郡,功劳卓著,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为国之虎臣。“西域亲附”作何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和平年月,辛庆忌完成一桩使西域亲附的大事,再具体说,就是辛庆忌作为汉使,前往于阗迎来一批古罗马人到张掖郡,并为之建县。这样解释有何不可! 因此,我认为骊靬县的具体建置人就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
“先生,你的这种分析有点捕风捉影了吧?”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遗案,有两类:一类证据确凿,另一类证据不全。历史学家为历史事件做出论断,不是为史料充足的事件去做人云亦云的复述或说明,而是为史料欠缺的事件做出合情合理而被后来历史证明正确的判断。正如一个高明医生去解决罕见的疑难杂症一样。要不,我们要历史学家干什么! 捕风捉影,正说明有“风”可捕,有“影”可捉。顺影寻去,影子后面难道不是事物的实体吗?张掖郡出现了一个骊靬县,而汉王朝远在万里之外的属国又有座骊归城,无论如何,不能视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既然有骊靬人归顺,就得给他们一个落脚处;有数千人,就应当建县。
五、虔人、羯、秦胡、卢水胡,原来都是骊靬人之称我们再来察看,骊靬县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中国史书对照面山下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做出了具体而又精彩的描述。骊靬人的生活画卷光彩照人。
《晋书》载:永和十年(354年),凉王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这是史书对骊靬人的最直接的描述。那些反对“骊靬即古罗马,骊靬戎即古罗马人” 之说的先生们,从未直面这段文字,从未做出追根溯源的探讨。
我们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统史书对于古凉州地区特别是河西的少数民族叙述中,总是会碰到这些民族概念:秦胡、卢水胡、力羯、虔人羌、骊靬戎,等等。其实,它们都是骊靬人的称谓。骊靬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东汉时期,中国称古罗马为大秦国,这没有丝毫含糊。因此,骊靬人被称作秦胡,也有时叫卢水胡或虔人。三国时期,骊靬人主要被叫作卢水胡,有时也叫秦胡。两晋及南北朝时期,被称作羯、力羯、骊靬戎等。
这不是胡说,有史为证,让我们一一道来。
先说羯。史书中东汉以前没有羯,东汉开始有了羯,或称羯胡,或称羯人,或称羯族。羯从何来?来自骊靬县。这是唐朝大学者颜师古告诉我们的。师古解释“骊靬”二字的字音时这样说:“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虔”字一字二音,照诚敬的意思读音为“前”,照掠杀的字义读音为“揭”。在这里读“揭”。骊靬,当地人自呼曰“力揭”,当地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我们不妨一试,念得快一些就是“力揭”,再快一些,就成“揭” 了。这样,骊靬县就成了“力揭”,骊靬人就成了“力揭人” “揭人”。怪不得当初王莽改骊靬县为揭虏县。于是“力虔”在演化中成为“羯”、“力羯”、“虔人”等。这些字,都是正统的读书人写的。因为是少数民族,就得写上带“羊”边的羯字了。《后汉书·西羌传》中,多处写到虔人羌,他们与其他羌族联合起来造反。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狼莫羌与虔人羌反,汉军在北地打败他们,“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指虔人羌一万一千人投降了邓遵将军。而《晋书》里对于羯人形象的描述更为具体,说他们“深目、高鼻、多须”(见《石季龙载记》)。“深目高鼻多须”的形状,正是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生理特征,也正是羯人即罗马人的人证。秦胡,即大秦胡的简称,有时叫秦胡,有时也叫大胡。在中国,东汉时期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后汉书》里写到秦胡的篇章有:
其一,东汉章和二年(88年),羌人反。羌豪迷唐率部与武威种羌万余骑,攻至塞下。护羌校尉邓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护迷唐于斜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这里,湟中指小月氏,秦胡即骊靬人。请注意,邓训是在凉州组织了这支军队,里面的秦胡来自凉州地区。(见《后汉书·邓训传》)
其二,同书《段靬传》记载:段靬是武威人也,从小就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好古学。做官就是武将。延熹二年,即公元159年,凉州有八种羌联合起来造反。朝廷任命段靬为护羌校尉,赴凉州去平叛。羌人起势凶猛,相继寇陇西、金城,以及河西四郡。并顽强抵抗汉军。凉州的秦胡骁勇善战。段靬率领以秦胡和湟中月氏为骨干的凉州兵,经十一年的战斗,才将羌叛平息下去。十一年,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建宁三年春,段靬凯旋回京,“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交给朝廷,请注意,武威人段靬部队中的秦胡仍然来自凉州地区。
其三,再看同书《董卓传》。董卓是陇西临洮人。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北地先零羌反,凉州的汉朝官员韩遂、马腾也相继跟着造反。大家知道,马腾是马超的父亲。他们杀了凉州刺史耿鄙,气焰甚盛。朝廷乃任命董卓为破虏前将军,任命一个叫皇甫嵩的官员为破虏左将军。皇甫嵩是凉州安定郡人。二人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平息了先零羌及韩遂、马腾的叛乱。董卓自恃功高,拥兵自重,朝廷调他到京城做大官,但董卓不肯丢掉兵权,借故不去,给皇帝上书说:“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董卓说,他想去,就是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及秦胡把他挡下了,他没办法,只好顺从。请注意,秦胡还是在凉州地区。
其四,我们再看《三国志》,在《武帝纪》中也具体写了秦胡。建安十六年(201年),西凉的马超与韩遂起兵反叛,洛阳大恐。马超离他老子的反叛隔了二十七年。老子的对手是董卓、皇甫嵩,马超的对手是曹操。曹操与之交战,开始屡屡受挫。
曹操说:“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他决定智取,施离间计。韩遂与曹操是老熟人,曹操要求和韩遂说几句话,于是在两军前,与韩遂寒暄片刻。后日,又相见。《三国志·注解》引用了《魏书》对这次相见的具体描绘:
“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惧。”
“可为木行马”,是说在前面架起粗木防护栏。这段文字,可以说写得绘形绘神,十分精彩。曹操的这一招也真灵,和韩遂说的不过几句随便的叙旧话,但引起马超怀疑,结果马、韩自相火并,导致失败。请注意,这些秦胡兵还是来自西凉。
上述文字,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写秦胡的仅有的篇章,也是所有史书具体写到秦胡的仅有的篇章。这些篇章明确告诉我们:秦胡就生活在西凉地区,是西凉生活的一个少数民族。这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秦胡到底生活在凉州的哪个地方呢?这里,就不能不讲到有名的卢水胡。说实话,对“秦胡”的概念,曾经有史学家做过另外的解释,但我们上面所举史实表明,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民族概念,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称呼。1976年,在张掖北部的汉居延遗址,发现两万多枚竹、木汉简,其中一枚上有六字“属国秦胡卢水”。属国指张掖属国。这句话说清楚,就是:张掖属国卢水地区的秦胡。秦胡生活在卢水地区。这汉简就是铁证。
而卢水地区又指哪一带呢?让我们走进《后汉书》和《三国志》所描绘的世界,里面的卢水胡会告诉我们:卢水就在骊靬县。不信请看:
其一,《后汉书·西羌传》说,建初二年(77年)夏,迷吾羌聚众反,“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说的是张掖属国管辖的卢水胡。很显然,卢水胡在张掖郡。
其二,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4年),汉明帝为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发七万兵力,从玉门关到雁门关这一条线上,分四路进击西域。《窦固传》中是这样写河西这一路的:“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胡,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很显然,这里说的卢水胡仍然在张掖郡。
其三,同书《邓训传》中说:“元和三年(86年),卢水胡反叛,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东汉光武时,武威郡治从民勤北迁到了姑臧。邓训是受命去平息卢水胡的。任务艰巨,情势紧迫,需快马加鞭火速投入工作。但这里,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乘驿车去上任的邓训,本应到张掖郡去当太守,怎么待在武威郡当起了张掖太守?其中究竟有何玄机?答案很明白,也很简单。因为出了武威西门,就是卢水胡的天下。姑臧以西是什么地方?是显美、骊靬、番和。反叛的卢水胡就聚集在骊靬一带,邓训只能在武威,实施他的平叛计划。很显然,卢水胡就居住在张掖郡的骊靬县一带地区,延及番和、显美。
其四,再看《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刚当上皇帝,卢水胡在伊健妓妾、治元多、封赏等人的领导下起兵造反,武威、张掖、酒泉的太守也率郡相应,河西形成割据之势。实际上这是河西人反对曹魏朝廷的政治起义。曹丕派镇西将军曹真率十万大军来镇压,又任命文武全才张既为凉州刺史,辅曹真军事。《三国志》对这次战争作了十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简要概括一下曹真、张既取胜的经过:(1)渡黄河从景泰直插武威、攻下武威,切断已攻到永登的卢水胡先锋后路;(2)诱敌深入,前后夹击,歼灭显美的卢水胡,俘虏万余人;(3)派新任的武威太守贯丘兴深入卢水胡大本营骊靬番和,说服卢水胡放下武器。书中写:“兴(贯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皆弃恶诣兴,兴皆安恤。”(4)安抚卢水胡后,迫使叛官张掖太守张进、酒泉太守黄华投降,河西遂平。此次平叛,历时二年,斩首五万余级,俘虏十万余,可见规模之大。请注意,《三国志》中这些文字,具体准确地告诉我们:卢水胡生活的大本营就是骊靬县,旁及番和、显美的一些地方。反叛队伍里当然也有不少汉民,但起事者头头是卢水胡人,书中只能概称为卢水胡。
其实,卢水就是今日的者来河。永昌地名普查时发现,当地老人仍把者来河上游叫早卢沟,即当年卢水河之意也。这就是明证:卢水就是者来河,它穿过番和,流入金川河。这就是卢水地区,万千异族生活在这里,按民族性讲,他们叫秦胡,按生活地域讲,他们叫卢水胡。汉简“属国秦胡卢水”,明确记载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自己疾呼曰力揭,王莽称他们为揭虏,提法又演化成羯人。
另外,《后汉书》还有两处提到卢水胡,一处是《西羌传》中,说:中平二年,烧何羌犯卢水胡,为卢水胡所重创,头人比铜钳率众去依附临羌县。临羌在今西宁附近。按此情判断,卢水胡重创比铜钳的地方,应该是骊靬县南山的北麓。再一处是《西南夷传》里提到的一句:“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黄石旧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北地即今宁夏吴忠市一带。这两地的卢水胡,是从河西东迁过去的骊靬人,缘由在后面细说。
在上面,我已向大家提供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具体写到卢水胡的全部文献史料,是忠实、直接地提供,没有断章取义,也没移花接木。之前的史籍中没有这个民族概念,以后,也只是在《魏书》中提到:北魏太平真君六年,一个叫盖吴的卢水胡人,在陕西杏城领导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自称天台王,最后失败。我想,任何人只要他忠实于那些历史文字的叙述内容,都不会作出另外的判断。
晋代,骊靬人在武威郡叫骊靬戎,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晋书·张祚传》中的有关记载。该传说:永和十年(354年),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晋代,骊靬县属武威郡。张祚在武威自立凉王,骊靬戎不服,揭竿起义,并打败了前来讨伐的和昊将军的部队。公元22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是卢水胡,时间过去13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又是骊靬戎,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恰好说明,卢水胡本身就是骊靬人。
好了,我们以时间先后做排列,做个小结看看骊靬县居民称呼的演变情况:
公元前48年一前45年,骊靬建县;对骊靬,当地居民疾言之曰:力(虔)揭,自呼曰:力揭人;公元8年,王莽改制,称骊靬为揭虏;公元88年,邓训在西凉发湟中月氏、秦胡、羌兵四千,出击迷唐;公元201年,马超率西凉秦胡反;公元74年,窦固率张掖属国卢水胡出征西域;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公元221年,武威太守贯丘兴到骊靬县和卢水胡谈判;公元354年,骊靬县的骊靬戎打败张祚的讨伐部队。结论:在中国的古罗马人叫骊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又被称之为揭虏、力羯、羯人、虔人、秦胡、大胡、卢水胡、骊靬戎等。
至此,我们不能不请出两位骊靬人皇帝和大家见面。他俩是谁呢?他俩,一个就是羯人石勒,另一个就是卢水胡沮渠蒙逊。前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赵,后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北凉。
石勒,山西上党武乡羯人,即骊靬人,字世龙,又名匐勒。有勇略、善骑射、自幼常代父亲掌管部落事务,为众所服。西晋太安中被晋军掠卖山东为奴,与一个叫汲桑的人聚众起义,一度攻取邺城,后兵败,投汉国刘渊为将,作战有勇有谋,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权位日重。大兴二年(319年)自建政权,号称赵王,史称后赵。据有冀、并、幽州及辽西一带。公元330年称帝,改元建平。在位期间,删减律令,立朝仪核户籍,定祖赋,兴学校,于诸郡立学官,办了不少好事。
沮渠蒙逊,张掖郡临松卢水胡人,也即骊靬人。其祖先曾在匈奴做过官。沮渠蒙逊初为后凉吕光部下。《晋书》说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才有英略,滑稽善权变,甚为吕光所器重。公元397年,叛吕光自立政权,史称北凉,据张掖,自称张掖公,改元永安。永安十二年,迁都武威,改称河西王。寻继灭西凉,占有西凉七郡,界连西域,在位32年。
六、古罗马人过黄河
既然卢水胡的家乡是骊靬,卢水是骊靬、番和一带,为什么黄河以东也出现了卢水胡,如北地卢水胡、杏城卢水胡?山西出现了羯人?道理很简单,河西骊靬人即中国的罗马人,到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发生过几次东迁的事,这是因为发生几次重大军事行动,简而言之,主要是:第一次,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西征魏嚣,时为河西大将军的窦融,率河西数万汉、胡步骑,以及辎重五千余辆,过黄河拜光武于高平(今固原),联合击败魏嚣,并将军队交给光武帝。窦融被封为安丰侯。这批投入光武帝统一大业的河西兵(自然有不少秦胡),战争结束后被安置于河东。
第二次,窦固征西域,率张掖甲卒及卢水胡出酒泉塞,战争结束后,部分被带回洛阳。
第三次,建宁三年春(170年),段靬率西凉五万秦胡步骑及汗血千里马回洛阳。
第四次,董卓讨平羌叛之后,被认命为并州刺史,他不放兵权,并把这支有骊靬人在内的西凉兵带到了山西,后被召入京,他又把部分西凉兵带入京城。
第五次,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韩遂反叛,带领以秦胡为骨干的西凉兵与曹操大战于潼关,最后曹操击败马、韩,并将俘获的西凉兵编入自己的部队。
第六次,三国黄初元年至三年,骊靬卢水胡反叛,镇西将军曹真率大军西征卢水胡,最后卢水胡败,曹真带十万俘虏回洛阳。
这六次,都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这些随军而东的西凉兵,年高退役后,基本就地安置,在那里繁衍生息,于是那里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即羯胡、卢水胡。
七、金关汉简告诉给我们什么
汉代有名的居延海在张掖以北,现在这里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汉代,这里是重要的边防关塞。1972—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两万多枚汉简。简册内容广泛,涉及汉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以屯戍内容为多,且保存了一部分汉代官方文献。这批简,又被称为居延金关汉简。已确定,它们在被埋时已经十分散乱,出土以后,年代及内容也颇多错乱。《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4版,公布了汉简中涉及骊靬内容的13枚,到底如何解读,还需要商榷。这13枚简,现全部抄录如下: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
简三:“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
简四:“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
简五:“□出钱五十,栗五斗,骊靬。”
简六:“靬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
简七:“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
简八:“出栗二斗四升,以食骊靬单门安。” 简九:“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
简十:“□过所遣骊靬禀尉刘步贤□。”
简十一:“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
简十二:“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
简十三:“骊靬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上列汉简,乍一看来,确实有点叫人眼花缭乱。有人看到简一中“神爵二年三月”六字,便啧啧说道:“骊靬建县与古罗马人无关,因为神爵二年已经有了骊靬县,神爵二年是公元前60年,古罗马人侵安息的卡莱战役发生在公元前53年。”
但是,请看清楚一点,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简文,毋庸置疑地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苑、县有天壤之别,前者是马场,后者是行政建制,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人一生的照片,放得无论怎样错乱,仍然能够从体貌上分辨出时间段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分辨出上列汉简的时间段。
如果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惊人的现象:它们清楚地分为骊靬苑、骊靬县两大类,凡是记录苑的,都牵连着番和县,凡是记录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苑内的工作人员,必然来自番和县,凡在县衙服差的,都和番和县无关;凡涉及苑的村庄,都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涉及骊靬县的村庄,也都和番和县无关。对苑、县的记录是如此泾渭分明。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清楚:苑跟番和脱离不了联系,是因为苑本身就设在番和县境内,所以勤杂人员必然也只能来自周围的番和县村庄,作为马场的骊靬苑不可能有自己的行政村;骊靬县跟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骊靬苑已从番和境内分割出来,以县份的面目出现,有了骊靬县自己的行政村,所以其当差人员不是来自番和而是来自骊靬本县。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无须假设,也无须估算,和骊靬有关的13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清晰地呈现出它们的真面貌。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属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简一、简二、简十一、简十二、简十三五枚,为一大类,属于骊靬苑时期的文书内容;简四等另外八枚,为另一大类,属于骊靬县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时间在前,骊靬县时间在后。前者表明,骊靬苑设在番和境内,故啬夫、杂役、牧奴等固然都来自番和,负责人为苑监;后者表明,从番和分割出来的骊靬县,以行政建制独立存在,人员再不需要从番和招募,自然要从骊靬本县的行政村招募来。负责人为县长。
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纪年简面目也清楚了,神爵二年为公元前60年,它明确告诉我们,此时只有骊靬苑,没有骊靬县,此简是骊靬苑时期的。换句话说,它明确告诉我们:公元前59年之前没有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的某年,骊靬神秘地以行政县的面目出现了。
西汉王朝为抵御外侮,在西北边郡建立养育军马的牧苑三十六所。祁连山下,番和之地,有丰富的草场,在番和境内建立马场,合情合理。之所以将番和的马场取名为骊靬苑,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之处。一则,骊本义就是黑马;二则,也许专门养育的是来自西域的胡马,故名;三则,也许体现西汉皇帝对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番邦的向往,故名。但问题是:为什么骊靬苑突然变成了县?为什么建县以后仍然坚持这个对人不尊的名字呢?而且,《汉书》告诉我们:西汉建县有一条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还为什么从民稀的番和县内切割出蕞尔之地另建起一个县呢?显然,其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不建置骊靬县,就不能最妥当地处理当时的特别事件,究竟是何特殊事件?这就是公元前48年至前45年之间,数千流亡在中国西界之外的古罗马士兵归顺西汉,他们正好来自遥远的骊靬国,番和县正好有个骊靬苑,这里过去是折兰王府,现在又是牧苑,设置条件具备,所以正好可以把这批人安置在这里,建县以领之,名字也无须改了。这不是“说曹操曹操到”,太有点巧合了吧?其实,无巧不成书,整个历史就是由无数巧合构成的。偶然构成必然。历史上“说曹操,曹操到”的事件还少吗?正是番和境内有个骊靬苑,后来归顺的骊靬人被安置在番和境内另建县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作者于2006年4月14日下午金昌市党校小礼堂做讲座。此稿是作者于2007年6月根据讲座稿整理而成。)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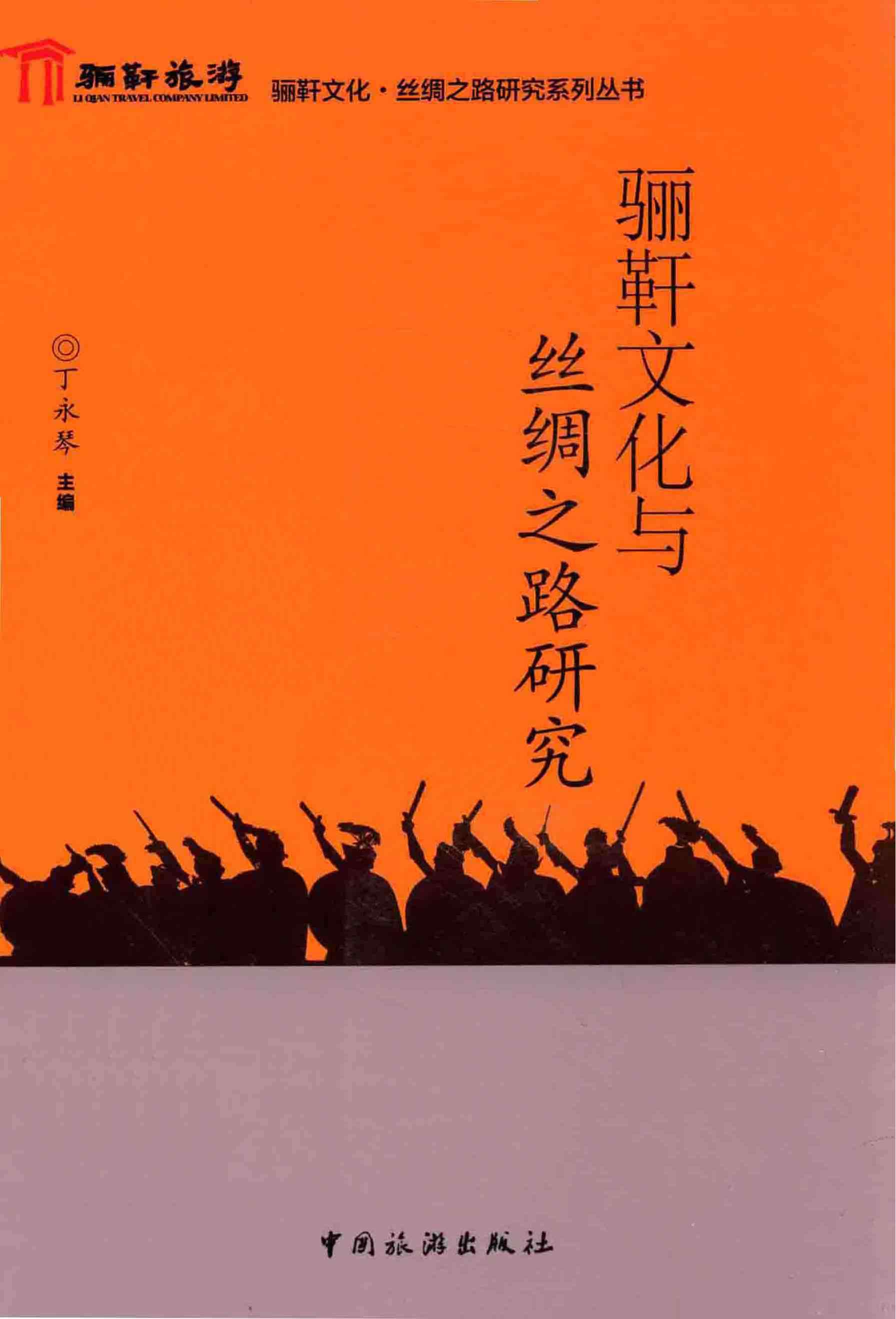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书分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骊靬文化旅游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研究、骊靬文学研究等四部分,收录了《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与战略定位》、《骊靬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展望》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王萌鲜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