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节选)
| 内容出处: |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30 |
| 颗粒名称: |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节选) |
| 分类号: | K203-53 |
| 页数: | 3 |
| 页码: | 8-10 |
| 摘要: | 文选自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的《汉史论集》。 |
| 关键词: | 文化研究 骊靬县 犁靬眩人 |
内容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其音义不类汉名,诸家注释,言各有殊,未能归于一是。前曾著文,稍加讨论,今复检阅,尚觉未安,故复论之。按骊靬县之名除见《地理志》外,又见许氏《说文》革部靬字下,云:“靬乾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改骊为丽,以靬训革。清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因其说,以为丽靬县之得名盖取义于丽皮,且以骊为误字,云:“《说文》,靬,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是许多氏所见《汉志》作丽字,盖取丽皮之意,以氏其县。若作骊靬,是以深黑色之乾革为县名也,于义无取。”揣《校注》之意,盖以骊靬县华丽之皮也,骊靬为黑色之皮也,而骊靬县当取义于华丽之皮。按骊训为深黑之色,亦见《说文》马部骊字,云:“骊,马深黑色;《校注》所言,即本乎此。”其字虽与丽有别,但因同声可以互用。《史记·周本纪》载申侯弑幽王于骊山下,《水经注》引其事作丽山,云:“遂败幽王于戏水之上,身死于丽山之北。”《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死,葬于骊山,《渭水注》引其事亦作丽山,云:“鱼池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左传》庄二十八年传载:“晋代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渭水注》引其事,于骊戎骊姬之骊均作丽,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冯迳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且《史记》之文,亦不尽同,一编之内,骊丽错举。始皇三十五年《本纪》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工,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此丽山即秦始皇葬处之骊山也。许氏于骊靬县之作丽靬,有类乎此,非有深意,《校注》必强分之,因而断言骊靬县之正文当为丽靬,且其得名之由来,乃取于丽皮之意,似有未合。至于许氏以骊靬县属于武威,而不属于张掖,《校注》未言及之。惠栋《读说文记》云:“丽靬,两汉皆属张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地理志》张掖郡骊靬,《郡国志》骊靬亦属张掖,许系之武威,未详。”王鸣盛《蛾术篇》云:“武威有丽靬县,骊靬前后《汉志》皆属张掖,疑许慎时曾改属,史失载。”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云:“《地理志》《郡国志》骊靬县属张掖,《晋志》属武威。此云武威者,《武纪》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许氏或据未分时图籍。”罗振玉《说文解字校录》引顾氏说:“丽靬,《地理》《郡国》二志属张掖郡,《晋志》乃属武威郡,或《后汉》此县即改隶,否则非许氏原文矣。近人辄谓此据汉武以前言之,恐无此理。”按东汉无骊靬改属武威之事。《后汉书·郡国志》载武威郡所属诸县,其自张掖郡划归者,仅有显美,未有其他。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征引颇详,亦未言及骊靬之并于武威。《汉书·张骞传》《注》引服虔语,亦言骊靬为张掖郡。虔为东汉末年人,上与许氏相接,相距不远,其间似不至有何变化。此盖因张掖、武威两郡毗连,县邑交错,易致混乱,许氏不慎,偶尔误引,必非别有他故。《蛾术篇》疑许慎时曾改属,是乃过信前人之说。《说文校议》又疑许慎所据为元鼎六年之图籍,更属虚臆曲解。许氏而后,曾注意及骊靬县者,即为服虔。《张骞传》有:“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靬、条支、身毒国”之语,《注》引服虔语曰:“犁靬,张掖县名也。”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犁靬之国发生关系。犁靬,张掖县名也。犁靬之国首见《史记·大宛列传》,作黎靬,《张骞传》改作犁靬;《西域传》又改作犁靬。《后汉书·西域传》又改作犁鞬,亦言亦名大秦。所举不同之名称,除大秦别有他说外,均属国音之异译,此乃历史上常有之事,不足为怪。服虔以西域国名当张掖之县,必有史实为其背景,惜未言明。师古重申服虔之说,但于所最关切之史实,亦未指出,云:“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声相近,清儒或有从此说者,其所发明亦鲜。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武威有骊靬县者,《两汉志》骊靬属张掖。”《汉书·张骞传》,抵安息,奄蔡、犁靬。服虔曰:“犁靬,张掖县名也”,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云;“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犁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按石州之说,足以破《地理志校注》说之惑,而于骊靬县得名之由来,亦较具体,然所以因其降人而置县者,亦阙而未详。熊得山译日人关卫《西方美术东渐史》第三章论《中国中原西方艺术之传播》,言骊靬得名由于犁靬国人之曾居于此地。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言张掖郡之有骊靬县,乃由处置归义降胡而设。1936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之《亚洲研究》第三四合期,内载卜德贝尔格一文,题为《中国边疆史札记二则》亦论及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其说与以上所言尽同。窃意骊靬置县,或与犁靬来华之人有关,而此辈来华之犁靬人,又当是《大宛传》所载安息进献之眩人。然必须证明安息所献眩人,果留华未返,且又确处河西,方能使此说信而有证。除以上所举二之外,论及此问题者,仍有数家。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以骊靬之得名,原于地理之形势,云:“今黑城驿在山丹县南。骊靬本属酒泉,与删丹人同时徙此。骊,俪也,靬音杆,射者所以杆臂,即拾也。故骊靬在今玉门县北百余里之华海子侧,有废城二,西有布鲁湖,接华海子,象两靬相俪也。”昔年,在成都,偶读蒙文通所著《周秦民族史》,内有《秦为戎族》及《秦即犬戎之一支》二文,言骊靬为山之异译,云:“《秦本纪》称申侯言:‘昔我先俪山之女,为戎胥靬妻,生仲,保西垂。’班固《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中国安得有天子曰骊山女,斯其为西戎种落之裔欤! ……骊山女在殷周间为天子,彼时西戎之强者,前则鬼方,后则犬戎,力足以侈天子之号,非此莫属。《秦本纪》言:‘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 《周本纪》言:‘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括地志》云:‘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十里。’《土地记》云:‘骊山即兰田山。’此骊山之名,与骊山女必有相联之关系。然殷周时西戎之天子,不容得在兰田,谅骊山原在西裔,此骊山之女号所由始。及其既入关辅,而新丰因有骊山之名,亦如陆浑之戎出瓜州,及既至伊川,而伊川之山以陆浑名,大荔在泾漆之北,及既至临晋,而临晋得大荔之名。《国语》云:‘幽灭于戏’,《左传》疏引《纪年》,亦云:‘幽死于戏’,则亦以犬戎之事,而后戏有骊山之名。是杀幽王之犬戎,即骊山女之族,亦即骊山女与秦皆犬戎这证也。骊山之后曰秦,亦犹《后汉书》言大秦国亦名犁鞬。犁鞬于 《张骞传》作犁靬,《匈奴传》作黎汗,《说文》作丽靬,皆一音之异译,骊山亦此之异译也。《汉志》张掖郡有骊靬,此当为骊山女为天子之所在,,于今为永昌县南,则固昔西戎地。古天子有骊连氏,或作骊畜氏,殆即作骊山女耶?”余前著《骊靬县得名之来原》一文,登载于《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以为祁连山为霍去病立功之所,甚为时人所注意,而其读音又与骊靬二字为叠韵,有通转之可能,因言骊靬之名,为祁连之别音,而骊靬县之得名,乃原于祁连。按此所录三说,吕调阳弊在过于推求字义,殊乏历史上之根据。蒙文通说,言之虽足成理,但亦有牵强附会之嫌。殷周间是否有骊山女为天子事,已属疑问,而骊山女为天子之地,又何以知其必在今甘肃永昌县南?汉开河西之地,建郡置县,又何以采用千数百年前空无着落民族之名,自不能不令人生疑。至于余之所论,亦有人认为不易成立。盖祁连之名,前书所载未有他称,汉人立县,何以不采用最习见之名称,而必用最生僻之骊靬二字,自亦难解。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
——本文选自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的《汉史论集》
——本文选自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的《汉史论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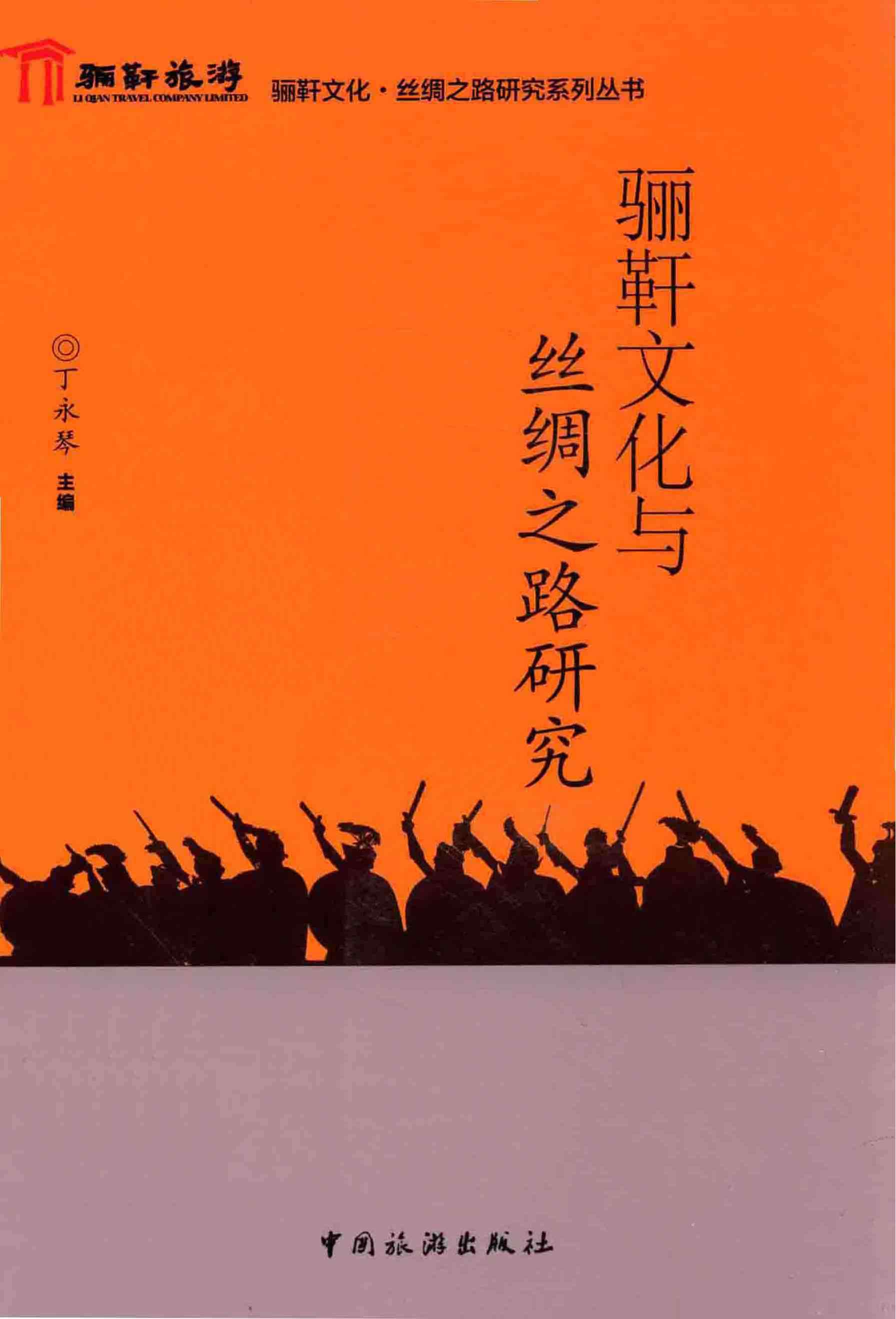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书分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骊靬文化旅游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研究、骊靬文学研究等四部分,收录了《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与战略定位》、《骊靬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展望》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张维华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