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
| 内容出处: |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28 |
| 颗粒名称: | 第一部分 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 |
| 分类号: | K203-53 |
| 页数: | 116 |
| 页码: | 1-116 |
| 摘要: | 本部分收录文章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节选)、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王萌鲜说骊靬、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骊靬故县与罗马降人、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研究等。 |
| 关键词: | 骊靬文化 文化研究 历史研究 |
内容
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
[美] 德效骞著 刘继华译
在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和县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用非常古老的中国对罗马称呼来命名的城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他们的城市起外国的名字。在那个清单上,有1500多个城市,只有其他两个城市使用外国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居住着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得出罗马帝国的人一定移民到了中国,并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似乎又不可能。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有着非常有名的丝绸之路,隔着4000英里的荒凉带,有沙漠和高山。横跨这条丝绸之路的是伟大的帕提亚帝国。这个国家对罗马的敌人充满仇恨,罗马从未征服过它。帕提亚人有效地阻塞了丝绸之路,从未允许任何罗马人自由地穿过他们的帝国。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通常允许贸易者的商队经过,但是他们阻止任何陌生人大量迁移。这座用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狭长的西北部。在公元前79年不存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是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的时候。也有名字由篡权者王莽命名,他用儒家思想来纠正名字,也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给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座城市他重新命名为揭虏(Jie-lu),这个词语包含两层意思:“在占领一个地方时拿下的胆小鬼【被俘虏】以及‘抚养的胆小鬼’”。然后,是不是中国人抓到一些罗马军团的囚犯,然后将其安置在中国西部边界以保卫边疆?古代中国将这座城市命名为骊靬(Li-jien)。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用来表示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后来用大秦(DA-TSIN)称呼罗马,中国政府同等对待这两个名字。骊靬这个名字是汉字对希腊名字“ALEXANDRIA”的抄写和缩写,本来表示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中国人不能区分罗马与亚历山大里亚。
在公元前110至前100年间,帕提亚国王的一个使团来到中国首都。在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当中,据说有来自骊靬的眩人。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眩人、舞者,无论男女都闻名于罗马世界。我们知道他们被送到国外。当这些人被中国人问到来自何处时,他们肯定地回答道“来自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单词自然地被中国人缩写为骊靬并用以表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关于罗马帝国和中国区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将欧亚大陆两端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60年,在罗马,罗马元老院将凯旋授予庞培(Pompey)将军。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到罗马,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助。恺撒(Caesar)和克拉苏(Crassus)来帮助他,并形成了第一次三人执政。恺撒在公元前59年成为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在公元前55年也成为执政官。后者后来成了叙利亚总督。克拉苏对三人执政贡献了大笔资金,这是其他两个人所缺乏的,但是他们的计划所急需的。同时他最缺乏和最想得到的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军事荣耀。他来到叙利亚之后,不顾他最好的将军的建议,向帕提亚人发动战争。公元前54年,他带着42000人进军帕提亚人的领土。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并不断发射一连串致命的箭。骑在马背上的帕提亚人在罗马人上来之前撤退,越过他们的马匹尾部发射,罗马人陷入无助境地。罗马军团只能形成一个方阵,在四周用锁盾来保护,这样就形成典型的罗马阵形——龟甲阵。但是帕提亚人朝罗马人盾牌的上、下方,毫无危险地屠杀了罗马人。到傍晚,20,000人被杀死,10,000人沦为囚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乘夜逃跑,到达叙利亚。我们不知道那些囚犯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迁至马尔吉安那(Margiana),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这是中亚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的梅尔夫(Merv)。这10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到马尔吉安那的安提阿(Antioch)的距离超过1500英里,俘虏在这样的行军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好的待遇。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古代诗人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迎娶了蛮夷妇女并服役于帕提亚军队。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中国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一个世纪,现在的蒙古被匈奴人占领,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人。他们的皇帝名叫单于。公元前60年,当他们的单于去世的时候,一场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导致8位请求者将自己立为单于。不久所有的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两个:单于呼韩邪(HUHANSIE)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郅支 (JZH-JZH)。当郅支在战争中打败了呼韩邪,后者从中国人中寻求援助,并派他的儿子给中国帝王做随从。中国的惯例是将结盟的外国王子控制在中国朝廷,一方面是作为他父亲良好行为的人质,另一方面是向他灌输中国文化和权力。郅支也派他的儿子来到中国朝廷。呼韩邪很礼貌地请求许可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朝拜,并表示其忠诚。他受到隆重的接待。宣帝很明智地把单于作为客人,并封他为与帝王一样的级别,位于中国人的王和其他高官之上。单于被给予丰厚的礼物,两个月后被护送回蒙古,在那里他被许可占领某些中国边远要塞。中国人支付高昂的费用以防止被匈奴人入侵中国边界。在这几年中,中国人因为呼韩邪的追随,送给他20000蒲式耳的谷物,这样他就能吸引大量的匈奴来跟从自己。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离开了蒙古,向西走去,试图与乌孙(WUSUN)联合,乌孙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或者吉尔吉斯人(Kirghiz)。然而他们杀死了郅支的大使,并将这个人的人头送到中国。郅支惊人地成功打败了乌孙的军队。但他不能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向北方前进并占领了现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国。1000英里的草原对匈奴来说不是很远,但比任何蒙古人以及其他草原骑士都远。
郅支认为在这里他会安全的。他于是向中国朝廷送了一封信,要求归还他那作为人质的儿子。守卫中国宫殿的校尉,谷吉(GUJI)(中国人的姓在前面,如匈牙利一样)负责护送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到达郅支王庭时,匈奴将谷吉和他的随从杀害了。同时康居(Sogdiana),中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郅支作为一个战士的名声很高,康居国王邀请他住在他的国家东部边界,在那郅支有着比寒冷的北方更肥沃的领土,能够保护康居免受乌孙的攻击。郅支害怕呼韩邪和中国人,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建议,签订了一个条约。康居送了数千骆驼、驴和马。然而在路上,旅行队遭受一场冻灾,只有约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康居。
国王对郅支表示欢迎并尊敬地招待,与他结盟,将他的女人送给他做妻子。郅支也将他的女儿送给康居国王。郅支现在深入乌孙国内,杀害乌孙人和让乌孙人成为奴隶,赶走他们的牛羊。乌孙不得不撤退,让他们西部的300英里国土无人居住。于是郅支变得骄傲,破坏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康居人。他为自己在都赖水(Du-lairiver)边建造一座有防御工事的都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塔拉斯河(RiverTalass),它的一条支流消失在锡尔河(Jaxartes)与巴尔喀什湖(LakeBalkash)之间的沙漠中。但是丝绸之路经过塔拉斯河,中国知道这座新城。中国本部西部有一位冠以西域都护头衔的官员,他有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自动化中国军队。当都护受中国皇帝命令出征时,在那个区域的小王国派遣军队予以帮助。
在公元前38年,西域来了两个年轻人,甘延寿做都护,陈汤为他的副手。甘延寿来自好的家庭,从未有过失。陈汤有进取心,勇敢,有计谋,但是不细心。
陈汤看到郅支单于在中亚发展一个大国的危险。他知道在本地辅助力量的帮助下,都护掌握的中国军队能够打败郅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获得安全保障,那将会太迟了。他的上级甘延寿赞同,但必须首先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远征的命令。然而陈汤指出这样一个请求会带来官方的耽搁,过于节俭的帝国朝廷将认为这样的远征太过昂贵。这时甘延寿病倒。
这对陈汤的诱惑很大。他大胆地伪造一个帝国的命令,要求臣属的政权派遣辅助力量,命令屯田的中国军队前来都护所在地开始远征。当甘延寿的健康好转,他了解到部下的行为,他感到吃惊,要求停止行动。但是事实上危险的行为即假造帝国命令的主要罪行已经犯了,不能够停止。因此在威胁和争论之下,陈汤说服他的上级来接受不灭的荣耀的机会。当一支40000人的力量集结,甘延寿和陈汤派人向东到朝廷送一个文件,谴责自己伪造帝国命令、集结帝国军队的罪过。在同一天,公元前36年的秋天,他们向西出发,前往撤回命令无法抵达的地方。
一半军队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路。另外一半在甘延寿和陈汤的带领下,走塔克拉玛干的北路,穿过乌孙国土来到伊塞克湖(LakeIssik-kol),然后向西。当他们进入康居时,陈汤与一些痛恨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达成秘密协议,这样获得有关郅支处境的关键信息。
汉语关于夺城的描述反映八个场景。这个描述一定来自绘画,和古代中国的图画一样,反映战利品、标明人和行动。不翻译原来的段落,这里我给出中国历史学家班固所写内容的大概。第一个场景:中国人的营地在距离单于都城1英里之处。城墙上挂着彩旗,士兵在喊:“过来打啊! ”城外骑兵飞驰,一百多名步兵采用鱼鳞阵排列在一个城门的两侧。
第二个场景:匈奴骑兵冲向中国营地,在营地的中国人竖起和装填好弩等待他们,在弩前,匈奴骑兵撤退。
第三个场景:中国军队在战鼓的推动下前进,团团包围城池,由大盾牌保护,射击城外的骑兵和步兵,他们正撤向城墙后面。一些人向城内塔上的守卫者射击,守卫者走下来寻求保护。但是从城外栅栏守卫者射杀许多进攻者,因此中国人火烧栅栏。
第四个场景:单于穿上他的盔甲,带着他的配偶和几十个女士爬上塔。所有人向中国人射击。但是进攻者击中单于的鼻子。许多女人被杀。单于也从塔上下来,登上一匹马,召集人到宫殿中战斗。
第五个场景:半夜过后。栅栏烧毁,余下的守卫者正逃人城中。一些人登上城墙,大声喊叫。城外和中国人四周有大批康居骑兵。一些人冲向中国人,被击退。
第六个场景:黎明时分。营地四周火在喷出。中国官员和人们在野蛮地呼喊,他们的钟声和鼓声震动大地。康居骑兵害怕,正在撤退。
第七个场景:中国人和联盟军在四周巨大盾牌的掩护下往城市推进。一些人已经进城。单于带着一百多男女,正跑进他的木质宫殿。
第八个也是最后的场景:中国人向宫殿放火,正努力争着进入。一些人进入,展开白刃战,已经致命地刺中单于。他的头被一名中国指挥砍下来。
现在我们仔细地注意这个记录的一些细节。首先,在第一个场景中有叙述一百多名步兵,采用鱼鳞阵排列在一个城门的两侧。“鱼鳞阵”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如此好的鱼鳞阵势的排列需要高度水平的训练和纪律。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或任何未开化的民族一定完成不了。牧民和野蛮人,像高卢人(Gaul)一样混乱地冲入战场。一个好阵形的排列只能由长期训练的人,比如专业士兵来完成。
这些人是希腊人吗?希腊人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离开大夏(Bactria)。而且马其顿方阵用小圆盾,大约直径一尺半。人们拿着它们难以足够紧密地挤在一起,出现鱼鳞的样子。
但是在那时罗马军团在步行的距离之内。他们靠战争为生。他们被一位著名的武士吸引,这位武士答应与痛恨的帕提亚人为敌。从阿姆河(Oxus)边帕提亚的边界到塔纳斯河边的郅支都城的距离为400~500英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以经典的罗马阵势——龟甲阵排列的人相距18年,这种阵法其他军队无法应用。长方形罗马盾的顶部的前面是圆形的,当一排士兵举着它们,靠在一起,一个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人以典型的中国人的视角从上面看确实像鱼鳞,除了罗马长形盾外,没有武器;除了罗马龟甲阵外,没有阵法能对中国历史学家的描述做出解释。
罗马人在郅支城的存在因重木城得到证实,中国人在城墙外发现重木城。希腊人不在城墙外使用重木城,但罗马人经常使用它们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前。那里的水上有一座桥。因此郅支明显在建筑防御工事时在工程学上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在他们给皇帝的报告中,甘延寿和陈汤陈述杀死1500人,相比郅支的配偶、后嗣、贵族和其他人,活捉145名俘虏,接受一千多人的投降,他们被作为奴隶分给为中国军队提供辅助的15个政权。当我们将活着的145人的数字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一百多的人数相比,我们几乎不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些145名罗马军团没有投降,但只是在他们的雇主被杀后停止战斗。他们可能保持阵形,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人群。他们实际上自由地选择跟随中国人。在中国罗马人相应地安置在一座专门建造的前线城市,对此中国人当然以他们对罗马的称呼——骊靬(Lijien)命名。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县城名单中,从王莽的命名中暗示居住在此的人是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获得,被抚养,这一切足以证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
罗马人影响的进一步证据是在事件中发现这次远征提交给朝廷的报告包括攻打的图画。这次胜利的记录能在我们读到的中国历史的编年史部分找到下面陈述:公元前35年2月,“因为单于郅支已经被处死……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现在关于“图书”展示给皇帝的女人的叙述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是何种物品,对于女士来说感兴趣?地图、君主的记录和类似文件肯定不会是后宫女性所寻找的事物! 这些女士几乎不能读书,这种文件太珍贵而不能由女人玩弄。一定是这次胜利的图画——班固以描绘场景的方式叙述战役确定了这个结论。
今天充足的证据表明前汉时期的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绘画艺术。中国将军穿越之前未知的道路的事实将有他们道路的地图。一幅去康居的路线图需要长布卷(尚未发明纸),附有沿途的风景的图画。关于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其他图画。
前汉时代的中国画,我们已经有许多描述,只是涉及名人、道德故事和传说。除了陈汤的报告我们知道没有当代事件的陈述。这些攻打郅支城的画在中国绘画中是前所未有的。它们说明中国艺术的一种新变化。
然而在罗马人的胜利中使用画是众所周知的。当陈汤与罗马军首领交谈时,这个人讲述了罗马人胜利的庆典。其中一些罗马人可能参加公元前60年庞培的胜利。关于维斯帕先(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的胜利,约瑟夫(Josephus)说:“战争有许多的陈述,在单独的部分,用一张关于有趣事件的、非常逼真的图画来展现。” 罗马人实践的描述非常符合陈汤放在路线地图上的图画的性质。而且这种关于生动地描述一场战争的记录在整个班固史书中是唯一的。
因此在公元前36年,陈汤在中亚遇见一百多名克拉苏罗马军团,将他们带回中国。远征的汉文记录以一个词语描述他们的军事组成,这在中国文学中别无其他,这只与罗马军队使用的龟甲阵相符。被中国人包围的匈奴城由重木城防卫,这不被中国人和希腊人所应用,但经常被罗马人应用。通过图画再现军事战争场景的实践被罗马人用于他们的胜利,但在中国前所未闻,这成为中国人远征报告的一部分。比其他任何事件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公元前79年和公元5年之间,发现中国有座城市有中国人对罗马的称呼——骊靬,这个名字表明该城居住着来自罗马帝国的人们。
中国的罗马城存在到公元746年,当时藏族人占领中国的那部分。1世纪之前,一个伟大的中国学者在中国的首都、位于中国西部的长安,他的著作说起那座城的人们对这个地名的特殊发音。他说那些人将这两个词的中文名混在一起,将它拼起来像“liakh-ghian”。他们可能在拼“Alexandria”中的“x”,“x”用中文拼不出来。因此罗马也为多种族居住的现代中国做出贡献。
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译自HomerH.Dubs, ARoman Cityin Ancient China ,GreeceandRome, Vol.4,No.2(1957),pp.139-148.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节选)
张维华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其音义不类汉名,诸家注释,言各有殊,未能归于一是。前曾著文,稍加讨论,今复检阅,尚觉未安,故复论之。按骊靬县之名除见《地理志》外,又见许氏《说文》革部靬字下,云:“靬乾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改骊为丽,以靬训革。清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因其说,以为丽靬县之得名盖取义于丽皮,且以骊为误字,云:“《说文》,靬,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是许多氏所见《汉志》作丽字,盖取丽皮之意,以氏其县。若作骊靬,是以深黑色之乾革为县名也,于义无取。”揣《校注》之意,盖以骊靬县华丽之皮也,骊靬为黑色之皮也,而骊靬县当取义于华丽之皮。按骊训为深黑之色,亦见《说文》马部骊字,云:“骊,马深黑色;《校注》所言,即本乎此。”其字虽与丽有别,但因同声可以互用。《史记·周本纪》载申侯弑幽王于骊山下,《水经注》引其事作丽山,云:“遂败幽王于戏水之上,身死于丽山之北。”《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死,葬于骊山,《渭水注》引其事亦作丽山,云:“鱼池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左传》庄二十八年传载:“晋代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渭水注》引其事,于骊戎骊姬之骊均作丽,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冯迳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且《史记》之文,亦不尽同,一编之内,骊丽错举。始皇三十五年《本纪》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工,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此丽山即秦始皇葬处之骊山也。许氏于骊靬县之作丽靬,有类乎此,非有深意,《校注》必强分之,因而断言骊靬县之正文当为丽靬,且其得名之由来,乃取于丽皮之意,似有未合。至于许氏以骊靬县属于武威,而不属于张掖,《校注》未言及之。惠栋《读说文记》云:“丽靬,两汉皆属张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地理志》张掖郡骊靬,《郡国志》骊靬亦属张掖,许系之武威,未详。”王鸣盛《蛾术篇》云:“武威有丽靬县,骊靬前后《汉志》皆属张掖,疑许慎时曾改属,史失载。”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云:“《地理志》《郡国志》骊靬县属张掖,《晋志》属武威。此云武威者,《武纪》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许氏或据未分时图籍。”罗振玉《说文解字校录》引顾氏说:“丽靬,《地理》《郡国》二志属张掖郡,《晋志》乃属武威郡,或《后汉》此县即改隶,否则非许氏原文矣。近人辄谓此据汉武以前言之,恐无此理。”按东汉无骊靬改属武威之事。《后汉书·郡国志》载武威郡所属诸县,其自张掖郡划归者,仅有显美,未有其他。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征引颇详,亦未言及骊靬之并于武威。《汉书·张骞传》《注》引服虔语,亦言骊靬为张掖郡。虔为东汉末年人,上与许氏相接,相距不远,其间似不至有何变化。此盖因张掖、武威两郡毗连,县邑交错,易致混乱,许氏不慎,偶尔误引,必非别有他故。《蛾术篇》疑许慎时曾改属,是乃过信前人之说。《说文校议》又疑许慎所据为元鼎六年之图籍,更属虚臆曲解。许氏而后,曾注意及骊靬县者,即为服虔。《张骞传》有:“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靬、条支、身毒国”之语,《注》引服虔语曰:“犁靬,张掖县名也。”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犁靬之国发生关系。犁靬,张掖县名也。犁靬之国首见《史记·大宛列传》,作黎靬,《张骞传》改作犁靬;《西域传》又改作犁靬。《后汉书·西域传》又改作犁鞬,亦言亦名大秦。所举不同之名称,除大秦别有他说外,均属国音之异译,此乃历史上常有之事,不足为怪。服虔以西域国名当张掖之县,必有史实为其背景,惜未言明。师古重申服虔之说,但于所最关切之史实,亦未指出,云:“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声相近,清儒或有从此说者,其所发明亦鲜。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武威有骊靬县者,《两汉志》骊靬属张掖。”《汉书·张骞传》,抵安息,奄蔡、犁靬。服虔曰:“犁靬,张掖县名也”,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云;“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犁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按石州之说,足以破《地理志校注》说之惑,而于骊靬县得名之由来,亦较具体,然所以因其降人而置县者,亦阙而未详。熊得山译日人关卫《西方美术东渐史》第三章论《中国中原西方艺术之传播》,言骊靬得名由于犁靬国人之曾居于此地。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言张掖郡之有骊靬县,乃由处置归义降胡而设。1936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之《亚洲研究》第三四合期,内载卜德贝尔格一文,题为《中国边疆史札记二则》亦论及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其说与以上所言尽同。窃意骊靬置县,或与犁靬来华之人有关,而此辈来华之犁靬人,又当是《大宛传》所载安息进献之眩人。然必须证明安息所献眩人,果留华未返,且又确处河西,方能使此说信而有证。除以上所举二之外,论及此问题者,仍有数家。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以骊靬之得名,原于地理之形势,云:“今黑城驿在山丹县南。骊靬本属酒泉,与删丹人同时徙此。骊,俪也,靬音杆,射者所以杆臂,即拾也。故骊靬在今玉门县北百余里之华海子侧,有废城二,西有布鲁湖,接华海子,象两靬相俪也。”昔年,在成都,偶读蒙文通所著《周秦民族史》,内有《秦为戎族》及《秦即犬戎之一支》二文,言骊靬为山之异译,云:“《秦本纪》称申侯言:‘昔我先俪山之女,为戎胥靬妻,生仲,保西垂。’班固《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中国安得有天子曰骊山女,斯其为西戎种落之裔欤! ……骊山女在殷周间为天子,彼时西戎之强者,前则鬼方,后则犬戎,力足以侈天子之号,非此莫属。《秦本纪》言:‘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 《周本纪》言:‘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括地志》云:‘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十里。’《土地记》云:‘骊山即兰田山。’此骊山之名,与骊山女必有相联之关系。然殷周时西戎之天子,不容得在兰田,谅骊山原在西裔,此骊山之女号所由始。及其既入关辅,而新丰因有骊山之名,亦如陆浑之戎出瓜州,及既至伊川,而伊川之山以陆浑名,大荔在泾漆之北,及既至临晋,而临晋得大荔之名。《国语》云:‘幽灭于戏’,《左传》疏引《纪年》,亦云:‘幽死于戏’,则亦以犬戎之事,而后戏有骊山之名。是杀幽王之犬戎,即骊山女之族,亦即骊山女与秦皆犬戎这证也。骊山之后曰秦,亦犹《后汉书》言大秦国亦名犁鞬。犁鞬于 《张骞传》作犁靬,《匈奴传》作黎汗,《说文》作丽靬,皆一音之异译,骊山亦此之异译也。《汉志》张掖郡有骊靬,此当为骊山女为天子之所在,,于今为永昌县南,则固昔西戎地。古天子有骊连氏,或作骊畜氏,殆即作骊山女耶?”余前著《骊靬县得名之来原》一文,登载于《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以为祁连山为霍去病立功之所,甚为时人所注意,而其读音又与骊靬二字为叠韵,有通转之可能,因言骊靬之名,为祁连之别音,而骊靬县之得名,乃原于祁连。按此所录三说,吕调阳弊在过于推求字义,殊乏历史上之根据。蒙文通说,言之虽足成理,但亦有牵强附会之嫌。殷周间是否有骊山女为天子事,已属疑问,而骊山女为天子之地,又何以知其必在今甘肃永昌县南?汉开河西之地,建郡置县,又何以采用千数百年前空无着落民族之名,自不能不令人生疑。至于余之所论,亦有人认为不易成立。盖祁连之名,前书所载未有他称,汉人立县,何以不采用最习见之名称,而必用最生僻之骊靬二字,自亦难解。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
——本文选自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的《汉史论集》
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
王宗维
骊靬位置应在条枝西北。《大宛列传》安息、条枝均有专条,而不列骊靬。《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记西志犁靬条枝接,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而不载到犁靬的距离。安息条记武帝时安息“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证明骊靬与安息相邻,此时成为安息的属部。证之条枝国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诸语,可知骊靬是一种民族,以其善于幻术著名,先是臣属条枝(塞流息咨王朝),条枝衰亡后,其一部分又成为安息的属部。安息极盛时的疆域,西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则骊靬人大概就在此西北。西汉武帝时汉朝使臣所到的骊靬,就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
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罗马国家的势力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比提利亚、本都王国,并于公元前64年前后消灭了塞流息咨王朝的最后势力,将其并入罗马尼拉领土,从此罗马与安息就以两河流域为界,安息役属下的骊靬人大部成为罗马的属民,罗马设立行省统治之。自此以后,汉朝政府与骊靬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了与罗马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汉朝与罗马就开始了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即罗马,汉朝人先是同骊靬人发生关系,从罗马统治骊靬后,汉朝又是通过骊靬与罗马政府接触,所以就产生了大秦又名骊靬的说法。这种不确切的说法,大概和东汉永元九年(97年)甘英出使地中海地区返回的报告有关。
骊靬人来中国,至晚从武帝元鼎年间已经开始。《大宛列传》说:“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汉使第一次至安息,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所派的副使,返回时间在元鼎三四年,安息献犁靬眩人,亦应在此时。由于汉武帝喜欢犁靬眩人的幻术表演,并令汉人仿效,此风更甚。《大宛列传》记:“及加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正义》释:“加其眩者之工,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犁靬。”说明梨靬眩人不但把幻术传入中国,而且汉朝迅速将这种幻术发展、提高,成为风行一时的技艺。这种眩人幻术,根据注释家的解释,相当于当今魔术。《史记索隐》引韦昭注:“眩人,变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息解。”《汉书·张骞传》应劭注:“眩,相诈惑也。”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通典》还记武帝时安息国所献犁靬幻人的体貌特征是“蹙眉、峭鼻、乱发、拳须”。这种特征,同《大宛列传》所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有所不同。由于骊靬幻人到中国受到汉朝政府的重视,所以后来陆续来中国者不少。西汉时张掖郡下辖骊靬县,《汉书·张骞传》骊靬条下颜师古注:“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又五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声,无定字。”骊靬的读音,颜师古注:“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由此可以说明,骊靬县的得名,与犁靬人有关。他们随西域各国使臣来汉,有的在河西待诏,不能返里,寄居在河西。因为他们善于幻术,所以远道来此寄居的西域各国人都被称为骊靬人,晋时称骊靬戎。汉朝政府为了进行管理,于其地设骊靬县。骊靬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更多地见于居延汉简中,大概在武帝后昭帝时,即有此县。骊靬人定居于河西,有的到达长安,虽然人数不多,但它说明西汉时汉朝已经和罗马东部辖境的骊靬人有着交往,骊靬幻术在汉朝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王萌鲜说骊靬
王萌鲜
一、两个伟大皇帝的憧憬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无独有偶,还有一句,叫相辅相成。小事物是这样,大事物也是这样。公元前1世纪,世界的西方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同一个时间,世界的东方也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西汉王朝。罗马帝国发展到恺撒、庞培、克拉苏“三巨头同盟”时代,已变得空前强大;同时,东方的西汉王朝发展到汉武帝中期,也变得空前强大。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亚、西亚传到了欧洲,也传到了罗马帝国。据罗马史学家卡希攸斯的著作记载,在一次向凯旋的将士授奖时,当恺撒大帝把中国生产的丝绸授给有功的将军的那一刻,几乎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这到底是什么呀?柔软而轻盈,坚韧而新颖,光滑而精致,颜色鲜,光泽斑斓。这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丝绸织品。恺撒说:这些东西来自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国家叫“赛里斯”,即“丝国”的意思。“赛里斯”这个名称也是几经翻译才传到罗马帝国的。老实说,中国的丝绸织品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高科技,犹如20世纪美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罗马皇帝十分神往东方遥远的大帝国,萦绕于心,情难自已,特别想跟这个神秘的东方之“丝国”取得联系。然而,有一个国家首先阻挡他们,这个国家,中国汉代称它为安息,即波斯国,今天的伊朗一带。安息把中国获得的丝绸等高新产品转手卖给古罗马,从中取得高额利润。这使罗马人十分愤怒,于是他们不惜发动战争打通走向中国的道路。古罗马皇帝对中国的相思之情何等深切!
遥远的东方大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传奇式地发展着。安息对罗马冷,对中国却特别热。汉武帝的特别使团到安息国界,安息王派官员及两万骑兵奔波数千里,到东界迎接中国使团,浩浩荡荡,经过数十城才迎接到首都,空前隆重。中国使团返回时,安息派使团一同前来,到中国后,向汉武帝献上大鸟卵和高级魔术师。汉武帝在金碧辉煌的甘泉宫里接见了安息国特使及高级魔术师。一听介绍,才知道高级魔术师的家乡,正是以前张骞提到过的骊靬,即古罗马。魔术师当场向汉武帝表演了口喷火、嘴吞剑的技艺,在这一刻,也使汉武帝和在场的所有中国官员为之目瞪口呆,震惊不已,随后都赞不绝口:神、神、神! 汉武帝向魔术师仔细询问了古罗马的国情及社会风貌。从此,这位中国皇帝对那个遥远的西方大国罗马,梦萦神牵,情有独钟。对待这位罗马魔术师也就特别宠爱和尊重,甚至每次外出巡行时,也一定要带上罗马眩人。这些历史场景,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以生动的笔调做了描述。
真是叫天天应,叫地地灵,中国皇帝和古罗马皇帝的历史情怀,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最初的憧憬结出了友谊之果,谁能想到,汉武帝去世四十年之后,竟然有数千古罗马士兵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中国,中国西北角竟然出现了一个以古罗马国名骊靬二字命名的县份。这个骊靬县的遗址就是今日永昌县的者来寨。
也许有人要问,真的有这个县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
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对骊靬县,中国史书有明确记载。
二、骊靬县,史书记载明确
对骊靬县,史书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或有关地理的篇章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记载。譬如《汉书》说:张掖郡辖县十个,有番和、显美、骊靬、鸾鸟等。这四个县都是永昌古县。当时番和城在今天的焦家庄,显美是今天的清河。有的史书某些文字还表明,骊靬县在番和城附近,靠祁连山。清代康乾时期编成的地理巨著《大清一统志》又十分肯定地指出: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城南者来寨。元代有《大元一统志》,明代有《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大清一统志》是前两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确认骊靬废县在者来寨之见,早于清代。
骊靬县到底建立于西汉何年?没有明确记载。但经过后来特别是现在一些学者的考证认定,它的建立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之间,或者说在公元前45年前后。后面我还要细说。它的撤销时间,史书倒是给予了明确的表述。《隋书》说:开皇中,即592年,隋文帝下令将骊靬并入番和,骊靬以县的建置存在630多年。《晋书》说,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这些文字,不是十分清楚地说明:骊靬县南依南山,北靠番和吗?这样的地方当然就是者来寨了。
那好,既然有这个县,永昌旧县志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某些老祖宗,特别是当时修县志的那些文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县的存在。我们知道,《大清一统志》,乾隆十一年完成的《五凉志》,都明确写了这个县,我们的旧县志乾隆本在编写时参照了《五凉志》,但却删去了骊靬县,为什么?一则,按字义解释,骊靬就是黑色的干牛皮,多可厌! 二则,骊靬又是一个西域番邦之国名,多可怕! 前者和牛联系,我们汉语中有多少美丽动听的词儿,先人偏偏用骊靬二字,后者和番邦联系,他们当然接受不了,删去为好。上世纪40年代,永昌陈世增又写了一个续修本,是手抄本,他明确写进骊靬县,遗址即今者来寨。
骊靬县的存在既已明了,那么,它又是为何而建的呢?这就是我要马上接着说的问题:骊靬探索之旅。
三、骊靬探索之旅
骊靬因何而建?史书正文都没有明确回答。但西汉王朝用这么两个古怪的字来作县名,必有它的深意在里面,不可能是随便而呼的。班固老先生在《汉书》中没有说明,就把难题留给了后人。于是后来的学者就开启了骊靬探索之旅。骊靬探索,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我分别说来。
第一个阶段,是发轫阶段,代表人物为应劭、服虔、颜师古。《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巨著,由于内容翔实,结构严密,文字赡富,很快被世人推崇,但也比较深奥,有许多地方读者弄不明白,于是不少人为之注解。注解者东汉末期最有名最有成就的是应劭和服虔,两人都是博览群书善著文的经学家,所生年代比班固晚七八十年。《后汉书》有他们的传。他们对骊靬县做了解释。应劭在他的《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服虔在注释中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东汉称古罗马帝国为大秦。又过了五百年,唐太宗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颜师古,对《汉书》做了全方位的诠释,他说,他的诠释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后来,也确实被历代推崇为最好的注释本。他解释骊靬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这三位先哲的话,连起来就是:以大秦国国名取名的骊靬县,是为到中国来的一批西域异族而建的。颜师古还特别指出:骊靬,当地居民自呼曰力虔。师古又特别指出,虔字此处读“揭”,就是说,居民自呼曰力揭,自称曰虔(揭)人,这可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实际上已揭开了一个特殊族种的谜底。后面将要细说。
第二个阶段是考证阶段。时间到了清代,大家都知道,满族建立了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界最黑暗残酷的时代。殃及全国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使文人们不敢说话写文章,文人们只好转头去研究古董。这样,事情的另一端出现了好现象:一个空前的考古、考证时期到来了,训古之风大兴,因此清代的古籍考究成绩非凡,为前代所不及。对骊靬的探索也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明确地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宣布:汉代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换句话说,骊靬县为归顺的大秦国人而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惠栋、钱坫、徐松、张澍、王筠、张穆、王先谦等,他们从康熙到光绪几乎囊括整个清代,对骊靬的考证形成了一个研究链。这些人,都是博览群书,学术造诣深,研究态度严谨而名载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像惠栋,是承前启后的大学者;像张穆,后人评价他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学,尤精西北地理文学,对历代各民族交往关系,考证精确,见解独到,极受学界推崇;像徐松,学界认为他对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卓著。这些学者一致认定: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此结论可以说是金声玉振,一字千钧。他们把应劭说的“西域蛮族”身份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了。
第三个阶段是开拓阶段。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新纪元,也为骊靬探索注入活力,注入新的文化元素。骊靬探索中出现了一批崭新的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文化运动,熟谙古今,学贯中西,思维活跃,视野开阔,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于一身,敢于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视自己所占领域的是与非,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发现新的境地,得出更精确的学术结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向达和冯承钧两位先生。
向达,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年至1938年,又到牛津大学、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冯承钧先生幼年出国,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尤精于中西交通史研究。二人都是学术巨擘,史界泰斗。不仅心中铭刻着中华泰山的庄丽,也目睹了欧罗巴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不仅对唐尧虞舜汉武唐宗研究透彻,而且步入希腊罗马殿堂窥其阃奥。因此,他们可以用更新的视角、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骊靬的本源。
向达在自己所著的《中外交通小史》一书中说:“中国史所记述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但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骊靬、大秦、拂森,都是指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向达先生明说了,骊靬县即为归义罗马人而设。冯承钧在他写的《西力东渐记》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匈奴,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罗马人从何而来?冯承钧认为,他们来自入侵波斯的古罗马军团,是失败后的古罗马军团的游勇散兵。这是一个大突破,说明公元前36年,流亡于中亚一带的罗马士兵,他们确系来自卡莱战役失败后的克拉苏的部队。他们徘徊在中国的西大门口。
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谦先生发表了自己的惊世骇俗的长篇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他在研究古罗马战争史的时候十分关注入侵安息失败后罗马大批流亡士兵的下落,终于从《汉书·陈汤传》中发现了他们部分人的身影。他得出了和冯承钧先生同样的结论:一支罗马部队参与了北匈奴郅支单于跟汉军的作战。汉军统帅陈汤把他们俘获后带入关内,在张掖郡设立骊靬县作了安置。德效谦之说,我们可以概括为“陈汤俘获说”。这是骊靬探索的第三阶段,是开拓,是突破,也是中西文化大交融后骊靬探索必然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是张扬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正本清源阶段。骊靬探索在第三阶段后变得悄然无声。时间进入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个年头。和西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空前深入。1989年下半年,《参考消息》及《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的消息,说的是:经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和几位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研究,认为西汉的骊靬县是为安置一批古罗马战俘而设的。他们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府副都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击败北匈奴郅支单于,俘虏了一批罗马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河西走廊,设置县城以领之。这其实是重申了德效谦之说,但在当时经媒体炒作,引起了靬然大波,震动了史学界。本人接着发表出版拙作《骊靬书——支古罗马军团的最后归宿》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尔后,中央电视台介入,《东方时空》、《走近科学》等栏目都多次报道,骊靬的话题推向世界,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但这些宣传和报道,都讲的是“陈汤俘获说”,由于“陈汤俘获说”存在致命的缺陷,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如葛剑雄、刘光华等教授的反驳,反驳的根据也在《汉书·陈汤传》中。因为《陈汤传》讲得十分清楚。书中说此次战役,“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也就是说,陈汤将军把所有的俘虏分赋给了参与汉军作战的十五个在西域的诸侯国,未带一人进关。这种反驳当然也是致命的,将“骊靬县与陈汤有关”的说法彻底击碎,所以“陈汤俘获说”,只能说陈汤的俘虏中有罗马士兵,但与骊靬建县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骊靬探索之旅到此止步了吧?不! 没有止步。“陈汤俘获说”只是探索中的一个分支,探索还正在深入。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常征教授,在1992年第一期的《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以翔实的史料,以严谨的分析,以学者应有的眼光和勇气,探讨了数千罗马兵归顺中国的过程。常征的结论是:古罗马军队在安息失败后,突围的第一军团六千多人辗转到了安息东的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并基本定居下来。公元前40年,大月氏发生“五翕侯”互并的大内战,被排斥的罗马人,越葱岭,傍昆仑山北麓进入河西,归顺汉王朝,另曰“义从胡”,汉王朝为安置他们而设骊靬县。因为他们是由大月氏国归顺的,我们把这一说概括为“月氏归义说”。
另外,不能不特别指出《辞海》关于骊靬的诠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有数百名学者参加,从1958年开始,到1965年完成修订,于1979年再修订后出版的百科综合大辞典《辞海》,在“骊靬”条目下解释道:“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这就是说,骊靬县,为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而建。这一说法,我们称为“骊靬内迁说”。
通过我们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已经明白,对于骊靬何以设县的探索,经过了四个阶段,即起步发轫阶段、深入考证阶段、开拓突破阶段、讨论张扬阶段。时至今日,骊靬何以建县出现了三种说法,即“陈汤俘获说”、“月氏归义说”、“骊靬内迁说”。同时,通过以上回顾,我们还得以明白:首先,对骊靬建县的探索已经过两千年时空,连绵不断,逐步深入,逐步明确,不是某些人说的“子虚乌有”;其次,探索中留下重要论断的人,东汉有应劭,唐代有颜师古,清代有惠栋、顾祖禹、张穆、王先谦等,现代有向达、冯承钧等,他们或者是训诂大师,或者是经学巨儒,或者是史地泰斗,他们一言九鼎之见,光照史册,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空穴来风”;再次,探索者们也许方法不同,叙述有别,但在认知上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骊靬即大秦国,大秦国即古罗马,骊靬建县绝对跟一批骊靬人有关,即跟一批古罗马人有关。汉武帝时期的骊靬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争论。但东汉时期,则认定大秦国即古罗马。《后汉书》说“大秦国一名黎靬”,即骊靬。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三种说法,首肯的当然是“骊靬内迁说”。一则,《辞海》是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的重点项目,是国家科技方面完成的全局意义的系统工程;二则,《辞海》的修订,投入了来自全国各界各领域的学术精英近千人,潜心研究,反复论证,去伪存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三则是它的修订,竟然经过了二十年沧桑岁月的洗练。因此,它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更大的精确性,更广泛的认知性。“骊靬内迁说”,涵盖了清代学者的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建的论断。降人不是指俘虏,而是指归顺、归化、归义、亲附。常征先生的“月氏归义说”和“内迁说”是一致的,不过说得更具体,认为这批骊靬人是从大月氏国越葱岭、沿昆仑山进来的。
四、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
是呀,说法种种,骊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或者说: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这里具体谈谈我的看法。讲四点:一、形势;二、时间;三、路线;四、具体办理人。
(一)形势:我们已经知道,古罗马帝国为打通走进东方的路线发动了对安息的入侵。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七个军团四万多人的部队进攻安息,结果在卡莱遭到安息骑兵的围歼,罗马兵有六千突围,一万被俘。这一万俘虏被送到安息东界守边。近两万罗马士兵稽留在中国西界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安息东界和大月氏接壤。被俘者被当作奴隶看待,不堪忍受虐待而大批逃亡,而沦为难民。突围的罗马兵则成为游荡在中亚盆地的游勇散兵。大月氏既是安息的友谊之邦,也是西汉王朝的友谊之邦。此时,穿过大月氏通向安息的丝绸之路,则显现出“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繁荣景象。汉天子广修文德,恩被天下,让四方来服。条条大路通向长安。西域都护府本身就有接纳归附者的重要任务。大批无家可归的古罗马士兵徘徊在中国西大门,进关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二)时间:指日可待,到底是何日?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德效谦,哈里斯等认定的公元前36年,另一个是常征先生认定的公元前40年,前者,我们前面已经说清,公元前36年陈汤俘获的罗马兵并没入关,已就地分散管之。后者,说的是已定居大月氏的罗马兵因大月氏内乱而逃亡中国,似亦理由不足。按照常理,已经定居,就有了起码的产业,起码的生活资料,不可能轻易离乡背井,弃家而逃。他们进入中国而又被设专县管理,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一是他们必须是流亡者,而不是定居者,只有流荡不定才会寻找栖息地;二是进关以后汉王朝为他们设专县,必须是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人数至少在两三千人以上,否则是不会设县的;三是他们在大月氏、康居等国流亡,时间不能长久,流亡时间过长,人员会自寻着落,队伍就会自行瓦解,也就没有了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卡莱战役是公元前53年,安息西界至东界相距约两千公里,突围的罗马兵团以及被俘的万余人转移至安息以东,需一两年时间;再经逃亡、流动和组合过程,又需一两年时间。这时,一支庞大的难民队伍已经形成。他们是一批职业军人,习惯于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他们与周围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出于生活的需要,必须组织起来;还由于当地居民或许对他们心存戒心甚至敌意,处处设防甚至要消灭他们,为渡过一道道难关,他们必须暂时结成一个群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体弱有病,或者有伤,不能奔波,只好留在当地听天由命了,而由强者结成的难民群体,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极力寻找着落脚安身的地方。因此,我们断定,数千古罗马兵进入中国,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最迟不超过公元前45年。汉骊靬县,就是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设的。
(三)路线:历史事件,总是会在史书中留下蛛丝马迹的。我们读《后汉书·西域传》,会在于阗国中发现一个十分新奇的地名:骊归城。《西域传》文字的叙述十分新奇地告诉我们:骊归城之名得于西汉。为何叫骊归城呢?顾名思义,骊归城就是欢迎骊靬人归顺的城市。可以想见,当年,西汉王朝的使者在这座城市举行了一个大会,欢迎数千骊靬人归顺中国,因为有重要的纪念意义,这座城市即改名为骊归城。丝绸之路南线经过于阗。流亡于西域的数千古罗马人就是从南道经于阗,进入阳关的。骊归城和后来出现在张掖郡的骊靬县形成惊人的呼应。骊归城成了古罗马兵进入中国的历史见证。
(四)具体办理人:班固的《汉书》为一个叫辛庆忌的人立了传。辛庆忌是狄道人,即现在的临洮人。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他就是张掖郡的太守,以后又到酒泉郡当太守。书中说他到张掖前并不知名,但到张掖郡当太守后,一下闻名朝野,成为名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书中这样写道:前在边郡,功劳卓著,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为国之虎臣。“西域亲附”作何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和平年月,辛庆忌完成一桩使西域亲附的大事,再具体说,就是辛庆忌作为汉使,前往于阗迎来一批古罗马人到张掖郡,并为之建县。这样解释有何不可! 因此,我认为骊靬县的具体建置人就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
“先生,你的这种分析有点捕风捉影了吧?”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遗案,有两类:一类证据确凿,另一类证据不全。历史学家为历史事件做出论断,不是为史料充足的事件去做人云亦云的复述或说明,而是为史料欠缺的事件做出合情合理而被后来历史证明正确的判断。正如一个高明医生去解决罕见的疑难杂症一样。要不,我们要历史学家干什么! 捕风捉影,正说明有“风”可捕,有“影”可捉。顺影寻去,影子后面难道不是事物的实体吗?张掖郡出现了一个骊靬县,而汉王朝远在万里之外的属国又有座骊归城,无论如何,不能视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既然有骊靬人归顺,就得给他们一个落脚处;有数千人,就应当建县。
五、虔人、羯、秦胡、卢水胡,原来都是骊靬人之称我们再来察看,骊靬县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中国史书对照面山下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做出了具体而又精彩的描述。骊靬人的生活画卷光彩照人。
《晋书》载:永和十年(354年),凉王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这是史书对骊靬人的最直接的描述。那些反对“骊靬即古罗马,骊靬戎即古罗马人” 之说的先生们,从未直面这段文字,从未做出追根溯源的探讨。
我们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统史书对于古凉州地区特别是河西的少数民族叙述中,总是会碰到这些民族概念:秦胡、卢水胡、力羯、虔人羌、骊靬戎,等等。其实,它们都是骊靬人的称谓。骊靬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东汉时期,中国称古罗马为大秦国,这没有丝毫含糊。因此,骊靬人被称作秦胡,也有时叫卢水胡或虔人。三国时期,骊靬人主要被叫作卢水胡,有时也叫秦胡。两晋及南北朝时期,被称作羯、力羯、骊靬戎等。
这不是胡说,有史为证,让我们一一道来。
先说羯。史书中东汉以前没有羯,东汉开始有了羯,或称羯胡,或称羯人,或称羯族。羯从何来?来自骊靬县。这是唐朝大学者颜师古告诉我们的。师古解释“骊靬”二字的字音时这样说:“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虔”字一字二音,照诚敬的意思读音为“前”,照掠杀的字义读音为“揭”。在这里读“揭”。骊靬,当地人自呼曰“力揭”,当地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我们不妨一试,念得快一些就是“力揭”,再快一些,就成“揭” 了。这样,骊靬县就成了“力揭”,骊靬人就成了“力揭人” “揭人”。怪不得当初王莽改骊靬县为揭虏县。于是“力虔”在演化中成为“羯”、“力羯”、“虔人”等。这些字,都是正统的读书人写的。因为是少数民族,就得写上带“羊”边的羯字了。《后汉书·西羌传》中,多处写到虔人羌,他们与其他羌族联合起来造反。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狼莫羌与虔人羌反,汉军在北地打败他们,“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指虔人羌一万一千人投降了邓遵将军。而《晋书》里对于羯人形象的描述更为具体,说他们“深目、高鼻、多须”(见《石季龙载记》)。“深目高鼻多须”的形状,正是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生理特征,也正是羯人即罗马人的人证。秦胡,即大秦胡的简称,有时叫秦胡,有时也叫大胡。在中国,东汉时期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后汉书》里写到秦胡的篇章有:
其一,东汉章和二年(88年),羌人反。羌豪迷唐率部与武威种羌万余骑,攻至塞下。护羌校尉邓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护迷唐于斜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这里,湟中指小月氏,秦胡即骊靬人。请注意,邓训是在凉州组织了这支军队,里面的秦胡来自凉州地区。(见《后汉书·邓训传》)
其二,同书《段靬传》记载:段靬是武威人也,从小就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好古学。做官就是武将。延熹二年,即公元159年,凉州有八种羌联合起来造反。朝廷任命段靬为护羌校尉,赴凉州去平叛。羌人起势凶猛,相继寇陇西、金城,以及河西四郡。并顽强抵抗汉军。凉州的秦胡骁勇善战。段靬率领以秦胡和湟中月氏为骨干的凉州兵,经十一年的战斗,才将羌叛平息下去。十一年,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建宁三年春,段靬凯旋回京,“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交给朝廷,请注意,武威人段靬部队中的秦胡仍然来自凉州地区。
其三,再看同书《董卓传》。董卓是陇西临洮人。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北地先零羌反,凉州的汉朝官员韩遂、马腾也相继跟着造反。大家知道,马腾是马超的父亲。他们杀了凉州刺史耿鄙,气焰甚盛。朝廷乃任命董卓为破虏前将军,任命一个叫皇甫嵩的官员为破虏左将军。皇甫嵩是凉州安定郡人。二人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平息了先零羌及韩遂、马腾的叛乱。董卓自恃功高,拥兵自重,朝廷调他到京城做大官,但董卓不肯丢掉兵权,借故不去,给皇帝上书说:“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董卓说,他想去,就是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及秦胡把他挡下了,他没办法,只好顺从。请注意,秦胡还是在凉州地区。
其四,我们再看《三国志》,在《武帝纪》中也具体写了秦胡。建安十六年(201年),西凉的马超与韩遂起兵反叛,洛阳大恐。马超离他老子的反叛隔了二十七年。老子的对手是董卓、皇甫嵩,马超的对手是曹操。曹操与之交战,开始屡屡受挫。
曹操说:“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他决定智取,施离间计。韩遂与曹操是老熟人,曹操要求和韩遂说几句话,于是在两军前,与韩遂寒暄片刻。后日,又相见。《三国志·注解》引用了《魏书》对这次相见的具体描绘:
“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惧。”
“可为木行马”,是说在前面架起粗木防护栏。这段文字,可以说写得绘形绘神,十分精彩。曹操的这一招也真灵,和韩遂说的不过几句随便的叙旧话,但引起马超怀疑,结果马、韩自相火并,导致失败。请注意,这些秦胡兵还是来自西凉。
上述文字,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写秦胡的仅有的篇章,也是所有史书具体写到秦胡的仅有的篇章。这些篇章明确告诉我们:秦胡就生活在西凉地区,是西凉生活的一个少数民族。这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秦胡到底生活在凉州的哪个地方呢?这里,就不能不讲到有名的卢水胡。说实话,对“秦胡”的概念,曾经有史学家做过另外的解释,但我们上面所举史实表明,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民族概念,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称呼。1976年,在张掖北部的汉居延遗址,发现两万多枚竹、木汉简,其中一枚上有六字“属国秦胡卢水”。属国指张掖属国。这句话说清楚,就是:张掖属国卢水地区的秦胡。秦胡生活在卢水地区。这汉简就是铁证。
而卢水地区又指哪一带呢?让我们走进《后汉书》和《三国志》所描绘的世界,里面的卢水胡会告诉我们:卢水就在骊靬县。不信请看:
其一,《后汉书·西羌传》说,建初二年(77年)夏,迷吾羌聚众反,“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说的是张掖属国管辖的卢水胡。很显然,卢水胡在张掖郡。
其二,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4年),汉明帝为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发七万兵力,从玉门关到雁门关这一条线上,分四路进击西域。《窦固传》中是这样写河西这一路的:“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胡,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很显然,这里说的卢水胡仍然在张掖郡。
其三,同书《邓训传》中说:“元和三年(86年),卢水胡反叛,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东汉光武时,武威郡治从民勤北迁到了姑臧。邓训是受命去平息卢水胡的。任务艰巨,情势紧迫,需快马加鞭火速投入工作。但这里,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乘驿车去上任的邓训,本应到张掖郡去当太守,怎么待在武威郡当起了张掖太守?其中究竟有何玄机?答案很明白,也很简单。因为出了武威西门,就是卢水胡的天下。姑臧以西是什么地方?是显美、骊靬、番和。反叛的卢水胡就聚集在骊靬一带,邓训只能在武威,实施他的平叛计划。很显然,卢水胡就居住在张掖郡的骊靬县一带地区,延及番和、显美。
其四,再看《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刚当上皇帝,卢水胡在伊健妓妾、治元多、封赏等人的领导下起兵造反,武威、张掖、酒泉的太守也率郡相应,河西形成割据之势。实际上这是河西人反对曹魏朝廷的政治起义。曹丕派镇西将军曹真率十万大军来镇压,又任命文武全才张既为凉州刺史,辅曹真军事。《三国志》对这次战争作了十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简要概括一下曹真、张既取胜的经过:(1)渡黄河从景泰直插武威、攻下武威,切断已攻到永登的卢水胡先锋后路;(2)诱敌深入,前后夹击,歼灭显美的卢水胡,俘虏万余人;(3)派新任的武威太守贯丘兴深入卢水胡大本营骊靬番和,说服卢水胡放下武器。书中写:“兴(贯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皆弃恶诣兴,兴皆安恤。”(4)安抚卢水胡后,迫使叛官张掖太守张进、酒泉太守黄华投降,河西遂平。此次平叛,历时二年,斩首五万余级,俘虏十万余,可见规模之大。请注意,《三国志》中这些文字,具体准确地告诉我们:卢水胡生活的大本营就是骊靬县,旁及番和、显美的一些地方。反叛队伍里当然也有不少汉民,但起事者头头是卢水胡人,书中只能概称为卢水胡。
其实,卢水就是今日的者来河。永昌地名普查时发现,当地老人仍把者来河上游叫早卢沟,即当年卢水河之意也。这就是明证:卢水就是者来河,它穿过番和,流入金川河。这就是卢水地区,万千异族生活在这里,按民族性讲,他们叫秦胡,按生活地域讲,他们叫卢水胡。汉简“属国秦胡卢水”,明确记载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自己疾呼曰力揭,王莽称他们为揭虏,提法又演化成羯人。
另外,《后汉书》还有两处提到卢水胡,一处是《西羌传》中,说:中平二年,烧何羌犯卢水胡,为卢水胡所重创,头人比铜钳率众去依附临羌县。临羌在今西宁附近。按此情判断,卢水胡重创比铜钳的地方,应该是骊靬县南山的北麓。再一处是《西南夷传》里提到的一句:“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黄石旧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北地即今宁夏吴忠市一带。这两地的卢水胡,是从河西东迁过去的骊靬人,缘由在后面细说。
在上面,我已向大家提供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具体写到卢水胡的全部文献史料,是忠实、直接地提供,没有断章取义,也没移花接木。之前的史籍中没有这个民族概念,以后,也只是在《魏书》中提到:北魏太平真君六年,一个叫盖吴的卢水胡人,在陕西杏城领导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自称天台王,最后失败。我想,任何人只要他忠实于那些历史文字的叙述内容,都不会作出另外的判断。
晋代,骊靬人在武威郡叫骊靬戎,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晋书·张祚传》中的有关记载。该传说:永和十年(354年),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晋代,骊靬县属武威郡。张祚在武威自立凉王,骊靬戎不服,揭竿起义,并打败了前来讨伐的和昊将军的部队。公元22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是卢水胡,时间过去13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又是骊靬戎,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恰好说明,卢水胡本身就是骊靬人。
好了,我们以时间先后做排列,做个小结看看骊靬县居民称呼的演变情况:
公元前48年一前45年,骊靬建县;对骊靬,当地居民疾言之曰:力(虔)揭,自呼曰:力揭人;公元8年,王莽改制,称骊靬为揭虏;公元88年,邓训在西凉发湟中月氏、秦胡、羌兵四千,出击迷唐;公元201年,马超率西凉秦胡反;公元74年,窦固率张掖属国卢水胡出征西域;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公元221年,武威太守贯丘兴到骊靬县和卢水胡谈判;公元354年,骊靬县的骊靬戎打败张祚的讨伐部队。结论:在中国的古罗马人叫骊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又被称之为揭虏、力羯、羯人、虔人、秦胡、大胡、卢水胡、骊靬戎等。
至此,我们不能不请出两位骊靬人皇帝和大家见面。他俩是谁呢?他俩,一个就是羯人石勒,另一个就是卢水胡沮渠蒙逊。前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赵,后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北凉。
石勒,山西上党武乡羯人,即骊靬人,字世龙,又名匐勒。有勇略、善骑射、自幼常代父亲掌管部落事务,为众所服。西晋太安中被晋军掠卖山东为奴,与一个叫汲桑的人聚众起义,一度攻取邺城,后兵败,投汉国刘渊为将,作战有勇有谋,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权位日重。大兴二年(319年)自建政权,号称赵王,史称后赵。据有冀、并、幽州及辽西一带。公元330年称帝,改元建平。在位期间,删减律令,立朝仪核户籍,定祖赋,兴学校,于诸郡立学官,办了不少好事。
沮渠蒙逊,张掖郡临松卢水胡人,也即骊靬人。其祖先曾在匈奴做过官。沮渠蒙逊初为后凉吕光部下。《晋书》说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才有英略,滑稽善权变,甚为吕光所器重。公元397年,叛吕光自立政权,史称北凉,据张掖,自称张掖公,改元永安。永安十二年,迁都武威,改称河西王。寻继灭西凉,占有西凉七郡,界连西域,在位32年。
六、古罗马人过黄河
既然卢水胡的家乡是骊靬,卢水是骊靬、番和一带,为什么黄河以东也出现了卢水胡,如北地卢水胡、杏城卢水胡?山西出现了羯人?道理很简单,河西骊靬人即中国的罗马人,到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发生过几次东迁的事,这是因为发生几次重大军事行动,简而言之,主要是:第一次,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西征魏嚣,时为河西大将军的窦融,率河西数万汉、胡步骑,以及辎重五千余辆,过黄河拜光武于高平(今固原),联合击败魏嚣,并将军队交给光武帝。窦融被封为安丰侯。这批投入光武帝统一大业的河西兵(自然有不少秦胡),战争结束后被安置于河东。
第二次,窦固征西域,率张掖甲卒及卢水胡出酒泉塞,战争结束后,部分被带回洛阳。
第三次,建宁三年春(170年),段靬率西凉五万秦胡步骑及汗血千里马回洛阳。
第四次,董卓讨平羌叛之后,被认命为并州刺史,他不放兵权,并把这支有骊靬人在内的西凉兵带到了山西,后被召入京,他又把部分西凉兵带入京城。
第五次,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韩遂反叛,带领以秦胡为骨干的西凉兵与曹操大战于潼关,最后曹操击败马、韩,并将俘获的西凉兵编入自己的部队。
第六次,三国黄初元年至三年,骊靬卢水胡反叛,镇西将军曹真率大军西征卢水胡,最后卢水胡败,曹真带十万俘虏回洛阳。
这六次,都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这些随军而东的西凉兵,年高退役后,基本就地安置,在那里繁衍生息,于是那里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即羯胡、卢水胡。
七、金关汉简告诉给我们什么
汉代有名的居延海在张掖以北,现在这里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汉代,这里是重要的边防关塞。1972—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两万多枚汉简。简册内容广泛,涉及汉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以屯戍内容为多,且保存了一部分汉代官方文献。这批简,又被称为居延金关汉简。已确定,它们在被埋时已经十分散乱,出土以后,年代及内容也颇多错乱。《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4版,公布了汉简中涉及骊靬内容的13枚,到底如何解读,还需要商榷。这13枚简,现全部抄录如下: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
简三:“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
简四:“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
简五:“□出钱五十,栗五斗,骊靬。”
简六:“靬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
简七:“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
简八:“出栗二斗四升,以食骊靬单门安。” 简九:“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
简十:“□过所遣骊靬禀尉刘步贤□。”
简十一:“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
简十二:“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
简十三:“骊靬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上列汉简,乍一看来,确实有点叫人眼花缭乱。有人看到简一中“神爵二年三月”六字,便啧啧说道:“骊靬建县与古罗马人无关,因为神爵二年已经有了骊靬县,神爵二年是公元前60年,古罗马人侵安息的卡莱战役发生在公元前53年。”
但是,请看清楚一点,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简文,毋庸置疑地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苑、县有天壤之别,前者是马场,后者是行政建制,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人一生的照片,放得无论怎样错乱,仍然能够从体貌上分辨出时间段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分辨出上列汉简的时间段。
如果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惊人的现象:它们清楚地分为骊靬苑、骊靬县两大类,凡是记录苑的,都牵连着番和县,凡是记录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苑内的工作人员,必然来自番和县,凡在县衙服差的,都和番和县无关;凡涉及苑的村庄,都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涉及骊靬县的村庄,也都和番和县无关。对苑、县的记录是如此泾渭分明。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清楚:苑跟番和脱离不了联系,是因为苑本身就设在番和县境内,所以勤杂人员必然也只能来自周围的番和县村庄,作为马场的骊靬苑不可能有自己的行政村;骊靬县跟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骊靬苑已从番和境内分割出来,以县份的面目出现,有了骊靬县自己的行政村,所以其当差人员不是来自番和而是来自骊靬本县。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无须假设,也无须估算,和骊靬有关的13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清晰地呈现出它们的真面貌。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属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简一、简二、简十一、简十二、简十三五枚,为一大类,属于骊靬苑时期的文书内容;简四等另外八枚,为另一大类,属于骊靬县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时间在前,骊靬县时间在后。前者表明,骊靬苑设在番和境内,故啬夫、杂役、牧奴等固然都来自番和,负责人为苑监;后者表明,从番和分割出来的骊靬县,以行政建制独立存在,人员再不需要从番和招募,自然要从骊靬本县的行政村招募来。负责人为县长。
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纪年简面目也清楚了,神爵二年为公元前60年,它明确告诉我们,此时只有骊靬苑,没有骊靬县,此简是骊靬苑时期的。换句话说,它明确告诉我们:公元前59年之前没有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的某年,骊靬神秘地以行政县的面目出现了。
西汉王朝为抵御外侮,在西北边郡建立养育军马的牧苑三十六所。祁连山下,番和之地,有丰富的草场,在番和境内建立马场,合情合理。之所以将番和的马场取名为骊靬苑,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之处。一则,骊本义就是黑马;二则,也许专门养育的是来自西域的胡马,故名;三则,也许体现西汉皇帝对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番邦的向往,故名。但问题是:为什么骊靬苑突然变成了县?为什么建县以后仍然坚持这个对人不尊的名字呢?而且,《汉书》告诉我们:西汉建县有一条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还为什么从民稀的番和县内切割出蕞尔之地另建起一个县呢?显然,其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不建置骊靬县,就不能最妥当地处理当时的特别事件,究竟是何特殊事件?这就是公元前48年至前45年之间,数千流亡在中国西界之外的古罗马士兵归顺西汉,他们正好来自遥远的骊靬国,番和县正好有个骊靬苑,这里过去是折兰王府,现在又是牧苑,设置条件具备,所以正好可以把这批人安置在这里,建县以领之,名字也无须改了。这不是“说曹操曹操到”,太有点巧合了吧?其实,无巧不成书,整个历史就是由无数巧合构成的。偶然构成必然。历史上“说曹操,曹操到”的事件还少吗?正是番和境内有个骊靬苑,后来归顺的骊靬人被安置在番和境内另建县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作者于2006年4月14日下午金昌市党校小礼堂做讲座。此稿是作者于2007年6月根据讲座稿整理而成。)
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
王萌鲜 宋国荣
古骊靬县的建立,与陈汤俘获的那批“战俘”有关,此说,引起部分史家学者的质疑,是无可辩驳的史实。但骊靬县确为一批古罗马人而特例建置,却也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和一些历史学家的探讨,论证如下:
第一,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中国的一批权威史书,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还指出: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第二,为骊靬降人设县有据可查。《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靬说:“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师古之解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所以如此,就在于它的可靠性。师古也许料到会有人怀疑他的注释,特地向后人交代说:他的注释“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师古语)。其实,早在以前,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这“蛮族”即骊靬人。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诂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涉足骊靬者不乏其人,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靬县取骊靬国名为县名,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中国从汉、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应、颜之说,“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只是由于典籍的大量失传,我们无法看到他们考证时所根据的材料。如徐松、为嘉庆编修,因坐事戍伊犁,致力于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北史地的研究,破疑解难,成绩卓著,为世所公认。现在有人武断地说这些学者结论没有根据,未免过于草率。现在还有人说:颜师古之解始于初唐,跟西汉中期六百多年,不足为凭。如果时间能够成为理由,那么,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距西汉两千多年,距初唐1400多年,更有何资格去评说或否定颜师古搞错了呢?正因为历史遥远,大量资料在不断遗失(这一点只要看看《汉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书目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就是凤毛麟角,如同长夜里的一盏小灯,只能守护,不能把它扑灭。因此,不能否定中国从东汉初唐到清末一批学者对骊靬研究的成果。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若干现代学者在这块土地上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不仅信心十足地坚持了应劭、颜师古之说,而且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前者如向达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后者如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
第三,确有大批古罗马人生活在河西。这批古罗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靬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靬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如《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189年),朝廷徵卓为少府,卓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腹上。”这里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就是湟中羌和大秦胡之意,后面的“羌、胡”就是“湟中义从及秦胡”的概语。秦胡确指古罗马人。有人认为,此处“秦”指汉人,假设如此,那么,下句的“羌、胡敝肠狗态”作何解释?汉人到哪里去了?再如,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曹操施离间计,约韩遂“叙旧”,以引起马超疑心。《魏书》具体记下了会语的情景。《魏书》说:“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防护木栏)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这《魏书》是曹魏朝廷编撰的皇家史,成书早于《三国志》,现在我们无法看到曹魏《魏书》,但这段文字却由南朝的裴松之抄录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注释中,十分可贵。这段文字,“胡”出现两次,前面点出是秦胡,后面就省掉秦字,正好说明“秦”是对该胡属性的限定。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有“属国秦胡卢水”的记载,“秦胡”纯属为民族之称,证据充分。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西汉初个别情况下也确称汉人为秦人,但秦人和秦胡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是两个概念。古史书中将汉人和少数民族并论时,总是讲“华夷”或“夏夷”,从未有过“秦夷”之称。那种把“秦胡”认为是汉、胡之合称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元人胡三省在解释《通》东汉章和二年邓训部中的秦胡时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此话大谬,章和二年,此时,建汉已三百年,历十二三代人之久,有什么秦威遗存?钦定的《后汉书》、《通》的著写者,又怎能以夷人口吻写史?秦胡即大秦胡,即古罗马人,实在没丝毫含糊处。
因为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靬人又称作卢水胡。骊靬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延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意即旧时之卢沟。《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靬、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靬戎造反之地。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因为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靬戎。《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靬戎”者虽属绝无仅有之笔。虽少,却实乃为铮铮发光,一字千钧的文字,须引起任何一个史学家的直面。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上确有数以万千计的被称为“秦胡”、“骊靬戎”或“卢水胡”的罗马人在河西生活。尽管他们在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本营却只有一处,即以骊靬县为中心,旁及番和、显美、临松县这一地区,即卢水地区。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第四,河西罗马人来自克拉苏东征军实属必然。西汉时期,中国跟罗马不存在商贸往来。甚至罗马使者也不能通达,自然谈不上罗马商人入汉。原因就是安息阻隔。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的:“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丝绸)与之交市,故庶阂不得自达。”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才有首批大秦使者到中国。那么,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答曰: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为争夺商业和领土,克拉苏发动了对安息的战争。通说克拉苏率五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1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一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14卷)。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 北靠康居, 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来往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响彻昼夜。那些在战场上逃逸的罗马士兵,以及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不堪忍受安息人欺辱的罗马俘虏,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从商道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靬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缘由。
具体完成这一重大行动的人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为陇西狄道人,仕途阅历并不复杂。少时随长罗侯常惠将军屯田乌孙赤城,汉元帝初,举茂材,拜为朝廷郎中车骑将军,寻迁张掖太守,时为初元元年(前48年),八年后迁酒泉太守,因“在两郡著功迹”,成帝初(前32年)征为朝廷光禄大夫,后为光禄勋,元延元年(前12年)去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班固在传中作了这么一段记述:辛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 此处的“西域亲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西域乌孙国时,不过是常惠部下小卒,无关轻重;后为光禄大夫时,管的是顾问应对之事,与西域无关,西域事由典属国掌管。辛庆忌到底是怎么在和平年代而使“匈奴西域亲附”的,答案就在张掖太守中。从时间推算,辛庆忌在张掖、酒泉两郡待了十六年,他在张掖的任期至少是八年,即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0年。《汉书·辛庆忌传》中说他在当车骑将军时“尚未知名”,而迁张掖太守后即“所在著名”,正是他作为朝廷的和平使者,奉命从西域大月氏等地接回要求内迁的罗马流亡军人,安置在他所管辖的番和县南照面山下。以此义举而扬名天下,而成为国家虎臣。从此,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使后人扑朔迷离的县:骊靬县。
第五,居延简的历史回首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有关骊靬的十二枚,尽管纷乱无序,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一惊人的历史现象:
凡是记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记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骊靬县的村庄,又都和番和县无缘,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后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角乐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兒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前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0年以后才出现的。
以西域的地名命名的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内以牧养西域进口的良马为主的国家牧场,地点在番和的城边。人们要问:为什么养马场在公元前50年以后某个时间突然变成县的建制呢?西汉立县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希则旷。” 为什么突然又在“民稀则旷”的番和腹地又另建县城呢?县城又为什么一定要以骊靬二字命名呢?为什么秦胡、卢水胡、骊靬戎偏偏一直居住在此地呢?很明显,建骊靬县,有其因时性,有其特殊性,还有其神秘性。它告诉我们:公元前50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附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谓骊靬人的古罗马人作为一个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靬县并入番和,骊靬存县600余年。
现在,有一个问题使学者们争论不休,即公元前36年,陈汤在对西域郅支匈奴讨伐中所获俘虏里到底有没有罗马流亡军人。这,只要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明白了。根据《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告诉我们的事实:郅支匈奴因屡杀汉使,深怕汉军联合南匈奴消灭他,便合众西迁,至坚昆;时康居国屡为乌孙所困扰,无力自卫。康居国王闻讯郅支西来,派使者至坚昆,答应给郅支在康居东边提供领地,欢迎郅支去驻,目的是将郅支作为屏障以胁乌孙。郅支大悦,移众继续向西。不料中途遇大风雪,数万之众死者十之八九,到康居东,苟活者才三千人,且伤兵者多。三千疲惫之旅,如何抵挡乌孙!郅支向康居王“借兵”,康居王借给郅支了一批人。这就是《陈汤传》中写的“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我们须特别注意“借兵”二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拥有六十万人口之众的康居不能自卫,郅支却靠从康居借来的“这批人”连续大败乌孙,致使乌孙胆寒,不敢西顾;不仅如此,郅支又乘胜骄,靠“这批人”反戈一击,一下子打得康居七零八落。郅支威震西域,成了一霸。“这批人”俨然如同神兵天降。很明显,这是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问题来了:“这批人”在康居那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又向康居反戈一击呢?我们可以断定,“这批人”在康居那里被视为异己,不受重用,为无用之徒,甚至受到歧视;而到郅支这边,疲惫中的匈奴自然要把他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力量。在康居那边他们是寄人篱下的睡狮,在郅支这边他们是腾跃下山的猛虎,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精通战术的战斗部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从安息西部草原上逃跑出来的克拉苏第一军团的部分,几经辗转而投靠康居。他们被借转而成为郅支匈奴的成员,并在后来参与了跟汉军的作战,形成罗马军人跟中国部队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触。首先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中国学者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提了出来。
有人说:“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已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 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克拉苏被重重包围,儿子为护父率军冒死突围在情理之中;克拉苏被俘,儿子为救父战死沙场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军团长战死,必有副军团长继任指挥,副军团长战死,必有另外的副手或下属继任指挥。这也是必然之事。“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显然是一句臆想之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大历史学家阿庇安告诉我们的:罗马军在卡莱战场上突围出了近一万人。为了活下去,这一万人必然要寻机奋力逃出安息,而较为松弛的安息东北边境为他们提供了出界的可能。何况安息首都泰西封就有商贸大道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陈汤俘获的匈奴中确有一批罗马军人。
无可否认,正如《汉书》记载,陈汤所获俘虏全部“赋予城郭诸国”。但《汉书》并未说这批俘虏就全部老死在那里,一直未做任何迁徙。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就可便知,古代环境为一个民族成批迁徙所造成的随意性和频繁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动辄南迁北移是常事。“赋予城郭诸国”的匈奴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断言他们就没有进入玉门关。他们跟骊靬县的建立无关,但却跟骊靬县的县民有缘。公元前48年前后,骊靬已在祁连山下拔地而起。
至于拿出个人对于“重木城”和“鱼鳞阵”的解释为根据,来否定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的部队同汉军作战的历史发现,更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说:“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这是一种臆想妄断。其一,不要忘记,公元64年毁于一场大火的罗马城,房屋基本上是用木料建造的,后建的新城才用石料取而代之,何况筑郅支城是公元前36年前的事,怎么能断然说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其二,倒退一步,就算是罗马军队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但是用兵之道,因势制宜,在彼处修石城者,不能说在此处不能修木城,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态势,罗马人协助郅支单于建造重木城并非天方夜话,惯于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穿起西装打起鲜艳的领带。我们大可不必为罗马人修重木城大惊小怪。
“否定论”者又说:“《陈汤传》中的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这又是一种妄断。他们解释说:“罗马乌龟阵是这样一种阵势。即军队进攻尤其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 这种解释,不攻自破。郅支单于的罗马人出于守城的需要,自然主要将盾牌挡在前面排成鱼鳞阵,演习防守的阵形,不需要“将盾牌高举过顶”的攻城阵形,因为他们眼前的形势是防御。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作战阵形主要承袭古希腊的作战阵形,以战士密集成列的方阵为基本形式,为着作攻防要求可以随时变换其形状。卤盾举过顶形成“乌龟壳”,或者卤盾不举顶而排成鱼鳞状,都是因不同需要而出现的形式变换,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拳击运动员出拳,出左手和出右手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硬要加以区别,而且是本质的只能使自己陷入荒唐。
至此,正如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辞海》在骊靬条目中诠释的那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在今甘肃永昌南。”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罗马城是为古罗马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古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
骊靬故县与罗马降人
宋国荣
骊靬,是西汉时期设在今永昌县境内的一个故县。有关骊靬县的设置,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多有记载和注解。唐初学者颜师古(581—645年)《汉书·张骞传》注解中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晋书·张祚传》载凉王张祚“……永和十年,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后汉书补注》、《二十五史补编·新斛地理志集释》、《大秦一统志》、《甘肃通志》、《乾隆府厅州县志》、《凉州府志备考》、《永昌县志》记载略同:“盖骊靬国人降,置此县以处之也。”“今凉州府永昌县南,本以骊靬降人置县,者来寨是其遗址。”1936年,中国首部《辞海》,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马部骊靬条均说: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在今甘肃永昌县南。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即此。《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按《隋志》开皇中并力乾县入番和,当即此县。”
清代学者惠栋(1697—1785年),在其著《后汉书》补注中说:“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王先谦(1842—1917年)在《汉书补》、《后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治经史,精于西北地理之学的张穆(石州1805—1849年)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嫠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钱坫(1744—1806年)、徐松(1781一1848年)、王筠(1784—1854年)等清代经史学家,考证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
1920年,史学家向达(1900—1966年)在《中外交通小史》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①中说:“汉代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又称之为犁靬,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别名。”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而汉时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之盛,于此也可概见。”1944年,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冯承钧在其著《西力东渐记》①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②所录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1907—1980年)《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提到公元前36年陈汤伐郅支时说:据现代学者考证,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北匈奴郅支单于既死,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遂统一匈奴。有关研究骊靬的历史学家和著述还有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1902—1987年)的《汉张掖郡骊靬县的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③;西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宗维(1934一)《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④;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毓棠(1911—1985年)《汉代的中国与埃及》⑥;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常征的《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件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⑤;法国学者L.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⑦;美国历史学家罗兹的《亚洲史·中国文明·中国和罗马帝国》等。他们都论证:骊靬县的设置与骊靬人来华有关。尤为张维华他在《汉张掖郡骊靬县的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中否定了自己前期著《骊靬县得名之源》⑧一文中提出的“骊靬为祁连译音”之说后说:“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现代史学家史念海在所著《河西集·河西与敦煌》中记述:“骊靬为县名,当是因骊靬降人而设置的。以域外降人设县,亦见于上郡的龟兹县,其县也是因龟兹降人而设立的,这在汉时已是通例,无足为奇。”
从上述历史经学家和学者对骊靬的解注中看出:骊靬县的设置是为安置从西域归降的骊靬人而设,古来就有记载,是有传承性的。并不是今人的所谓发现。
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谦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当时应历史条件的制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9年,时在甘肃省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通过法新社在新华社《参考消息》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一文(见1989年12月15日)。同月3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内容更详细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许多媒体和学者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但,这里并没有发表哈里斯等人学术上的任何东西,为此,学术界持根本的否定态度。
缘由是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等学者研究认为:公元前54年,古罗马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4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安息(今伊朗东北),第二年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克拉苏被杀,只有部分军团士兵突围逃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尔莱战役。这些逃出突围的罗马人后来流落到西域的乌孙、康居等国做扉佣军。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联合康居、乌孙等西域15国兵讨伐匈奴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发现一支奇特的部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他们认为,这里的“鱼鳞阵”和“重木城”只有罗马军队采用。而这些使用“鱼鳞阵”和“重木城”的士兵就是克拉苏兵败后逃亡西域,后来依附匈奴郅支做雇佣兵的罗马士兵。这次战争汉朝军队获胜,西汉政府便设了骊靬县来安置这批罗马战俘。
十余年来,永昌的骊靬古县,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专栏于2001年7月15日,在永昌骊靬村作了现场直播。中国的香港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甘肃电视台,还有西班牙、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外的电视台都来永昌拍制过有关骊靬的专题片。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德国的《镜报》、波兰的《共和国报》、法国的《欧洲时报》等中外百余家报刊对永昌骊靬古县和骊靬降人进行了报道。
骊靬古城为罗马战俘而设,也就是与甘延寿、陈汤俘获的战俘有关一说,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因《汉书·陈汤传》中记载,汉军伐郅支匈奴所俘获的千余战俘都“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根本未被汉军带入玉门关,跟骊靬城的设置没有关系。为此,一些学者根据新闻报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提出质疑和商榷的观点。其主要有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对此说有感而写的散文《天涯何处骊靬城:读书献疑》①,北京大学教授杨共乐的《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德芳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②等,学者们通过研究史料对骊靬城与罗马战俘的关系提出质疑和否定。
近年来,虽然人们在骊靬上热情不减,但争论的焦点还只是一个“古骊靬城与骊靬降人是否有关”。其中存在的疑点还需要有关专家学者探考研究和商榷。如果把学术界、媒体报道中的一些人和事,拿来做否定骊靬县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理由和论点。显然是不妥当的。
骊靬县与骊靬降人,在历史上千百年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汉唐时期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会点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具体反映,它对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往,中华民族的发展形成,彰显中华大国文化深厚积淀的强大包容性和独特人文魅力,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永昌经济社会,提升地方知名度,开发旅游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价值。研究和保护性地开发骊靬,不但是永昌县的大事之一,更是甘肃省的一件大事。
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研究
刘继华
德效骞,英文名为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于1892年3月28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Deerfield),是近代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早年跟随父母来华过颠沛流离的传教生活,青年时出于宗教热情来华当过基督教传教士,并出于传教目的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从此走上汉学研究之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 Chicago)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马歇尔学院(Marshall College)、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ofLearned Society)、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及其神学院、太平洋学会(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中研究汉学,在汉学界声誉日隆,最终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①,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他是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最早提出者,因此要厘清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渊源,他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本文对他的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推进骊靬文化研究的开展。
德效骞首次提出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时间为1940年,而不是许多论著所言的1957年。在1940年,他在杜克大学及其神学校任教,于著名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了《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AMilitaryContactbetweenChineseandRomansin36B.C.”)一文。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与另一位教授的研究有关,这位教授是荷兰汉学家戴闻达。
一、戴闻达与德效骞关于郅支之战的讨论
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一1954年),1889年出生于荷兰哈灵根(Harlingen,Netherlands),起初在莱顿大学学习荷兰语文学,不久跟随因著有六卷本《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而闻名的荷兰汉学家、人类学讲座教授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年)学习汉语,1910—1911年在巴黎又受教于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年)、高迪爱(HenriCordier,1849—1924年),奠定坚实的汉学基础。他于1912—1918年来华担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翻译,1919年在莱顿大学作为汉语讲师开始学术生涯,1930年成为莱顿大学教授,并成立汉学研究所(SinologicalInstitute)①。他因翻译《商君书》(TheBookofLordShang)和研究《道德经》而闻名,曾担任《通报》的共同主编(coeditor)②,为荷兰汉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戴闻达于1938年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十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西汉史上一次有插图的战争记载》(“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inthe 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③,该文对《汉书》中所记载的郅支之战进行了翻译,并进行了解释。该文经过充实、修改后,于1939年发表在《通报》上。这篇文章引起德效骞关注,他认为戴闻达推断出陈汤带回他进攻单于城市的图画,并且这些图画在皇帝的宴会上引起浓厚的兴趣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存在陈汤应该有描绘自己获得大胜的图画许多理由,比如陈汤有矫诏出兵之罪,他必须尽可能地取悦皇帝和宫廷以减轻罪责,于是他将图画与他的报告一起呈送朝廷,而这些图画可能会取悦于朝廷。德效骞认为在古代行军中,中国将军进入未知疆域存在绘制地图的事实,并以李陵带兵征讨匈奴为例。
当他(李陵——引者注)前行(在他被匈奴攻击之前)时,他对旅行过的地方绘图。文献(《汉书》卷54)说当他到达他的军队进入匈奴疆域最远的地方,“他停止,扎营,在地图(图)上记录山水和所经之地的构造。他派遣麾下骑兵陈步乐回(到汉人地界)以便(后者)可以报告(给武帝),送这些地图。步乐(然后)被皇帝召见”④。从这段记载,似乎制图是武帝及之后远征军的一项一般性项目,为此中国将军带着会画图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画家。如果制图是中国远征军一项公认的功能,被陈汤送回的图画的制作者可能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另一事件似乎证实这一假设:陈汤的军队没有在康居人的疆域浪费时间,而是直接进攻单于。康居人表面上敌对,因为他们与单于结盟,以至于陈汤不得不用俘获那些前来引导他的人为借口,来说明他们出现在他的军营。郅支单于已经因其横暴而得罪许多康居人,所以他们想帮助中国人,但因为他们的联盟,他们不敢公开这样做。因此在战争前极不可能的是有一个康居人在中国军营。他可能在后面跟随,但他几乎不可能画这场战争。①
从上述引文可看出,德效骞得出制作地图是汉武帝及之后中国远征军经常性的事务,由此进一步推导出,陈汤军中的画师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并以康居人因与匈奴结盟为依据证明康居人不可能是反映郅支之战图画的制作者。他认为古代中国地图上有反映地方情况的图画,由此提出从中国到康居的地图一定是一张长卷,而在两边则有许多空白之处,对这些空白之处,他认为画师会用汉军进攻郅支单于的景象来填充。
一张长途的画,从中国疆域到康居,一定是张长卷,有许多空白地方在两边,代表遥远的路途。对于一名画家而言,自然会用对单于城的辉煌进攻的激动人心的景象来填充一些空白地方。一个令人想起的例子是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他年轻时在美国政府服务,他镌刻的地图上刻上了海鸥(因此他被解雇)。因此这些地图成为陈汤送给朝廷报告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图画,当然这些图画引起家里人和宫廷妇女的关注。② 利用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的事例,他推导出画师会在地图上画上郅支之战的情景,由此陈汤上报朝廷的地图上有反映郅支之战的画,这些画引起国人和宫廷妇女的兴趣。接下来,他对戴闻达使用的一个短语提出质疑。
你(即戴闻达——引者注)翻译中的一个短语,我大胆挑战,特别是因为它加强你对图画的假设。在第259页第9行,在描绘单于门外步兵的地方,你翻译为:“lineduponeither side of the gate ina formationascloseas thescalesof afish.”在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 closeas”。我认为宁愿用“afish-scaleformation”。我由它想到希腊人重叠盾牌的行为,这叫作过度防护(Over-shielding)。这样一个战争排列自然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对他们来说它是陌生的。康居人可能从以前征服他们的希腊人那里学会它,特别是因为它曾有效地打击自己。这样一种排列无益于反对中国人的强弩,它能射穿任何盔甲。画家看见这种阵势将会把它带入画中,作为他注意到的奇异风俗的一个典型。在另一方面,它不可能进入书写的报告,因为它对没有见过它的中国人没有意义。因此这个短语“鱼鳞阵”很有可能来自一幅画而不是来自报告。我想知道如果陈汤地图上的图画不是严肃的雕刻:一系列小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分别被边界隔开,以致该系列给予战争的一系列场景。然后这个新的特征,如果有的话,在一个组成的画中对一个复杂的事件不做如此多的分析,而只是一系列画,组成一个连续,去讲一个故事,像ChinMi-ti下跪的情景和同样的人渴望地看着雕像(你的第253页底下的第4个注释)。画家自然以这种方式看一场战役。你的记载将组成半打图画。
① 他认为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closeas”,用“afish-scaleformation”即鱼鳞阵更适合原文的意思,并将鱼鳞阵与希腊人的叠盾行为相似,认为这是征服过康居的希腊人留给康居人的影响,而这种阵势无法抗击中国强弩的进攻,但却作为奇风异俗而引起中国人的注意,鱼鳞阵来自画而非报告。他认为陈汤地图上的画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讲述着郅支之战的故事。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所作的评论非常重要,接受了他关于图兼有图表、图画双重意义的说法,认为这比自己的本来想法更具说服力;同意德效骞所提出的古代地图上会在相关地方添加图画予以注释的意见,认为反映郅支之战的六幅画是一个系列,一起说明郅支之战的故事发展进程。
德效骞博士的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在这个图中确实更像兼有图表和图画的意思,这甚至比我起初的想法更令人满意。我们的古代地图不反对在它们上面对地方添加图画般的注释。我非常同意这些图画组成一组,一起说明故事的发展。这是我在论文中的意思即使我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这个意思。它们被边界隔开或它们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合成物,多种元素显示事件的连续发展。我们没有方法知道。德效骞教授的建议即步兵的鱼鳞阵势可能与希腊风格的阵法复合盾有关是特别有价值的。然后这些步兵一定是康居人而不是匈奴人。这是希腊对该地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证。②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提出的鱼鳞阵与希腊风格的复合盾阵法相关的想法非常具有价值,这是希腊文化对康居地区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当然,戴闻达并非完全赞成德效骞的想法,他认为画师不一定是中国人。不过他不会计较于画师的国籍,他认为“不管画师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幅公元前35年存在的画的事实是不同寻常的重要,它与编史的联系依然非常重要”③。
二、德效骞的《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
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据其自己交代,目的有二:一是为戴闻达教授关于郅支之战的研究提供佐证,二是更正自己之前对这场战争所发表的评论。
他在文中首先提出应该注意研究描述郅支都城的防卫者的特定词组,《汉书》中“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中的“鱼鳞阵”一词自然会提出关于能够摆出如此复杂阵势的军队的类型及其国籍的问题。
我(德效骞——引者注)提出特别的短语来研究郅支首都捍卫者的描述。中文记录描述“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现在“鱼鳞阵”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物,它自然引出关于能执行如此复杂军事策略的军队的特征和国籍问题。这些士兵必须制定这样一种方式,以便他们挤在一起并且将他们的盾重叠在一起。成功地完成这一壮举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这样有序的事情不是与匈奴一样的任何游牧民族所能够办到的),意味着较高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在这些士兵身上可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训练。牧民、蛮夷和高卢人一样混乱地冲进战争;鱼鳞阵的方式需要纪律和训练;只有职业士兵在面对攻击的时候才能成功地运用它。①
他认为鱼鳞阵是个非常复杂的阵法,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需要经过较高文明教育的士兵,而且这些士兵需要经历长期的军事训练,由此他提出这个阵法所需要的纪律和训练不是匈奴等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游牧民族不具备实践鱼鳞阵的条件,只有职业士兵才能运用它。那么职业士兵的国籍是什么呢?
我(德效骞——引者注)首先猜想这种阵势是陆龟或龟,罗马人常用来攻克堡垒。他们将盾举过头以保护他们免受飞弹落到他们身上。但是都赖水距离任何罗马领土都非常远;它在咸海东部,大约在东经71。北纬43°。即使Praaspa,公元前36年在安东尼的领导下,罗马人突破的最远的东面距离仅在东经46°。在中文记录里没有进一步提到盾在士兵头上。因此我得出结论,自从希腊人征服康居,这些士兵必定是希腊人。所以我被误导了。②
德效骞在思考鱼鳞阵时,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士兵在进攻堡垒时所用的龟甲阵 (testudo),但郅支城在都赖水旁,距离罗马帝国领土遥远,由此他排除了罗马
① HomerH.Dud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4-65.
②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p.65.
人而认为是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的可能性大,他们曾经征服康居,但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成立,并提出结论不成立的原因。
但是希腊人的大夏(Bactria)在公元前141年和前128年之间,很可能在公元前130年,大约在陈汤远征之前的一个世纪,被蛮夷打败。此外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明白在那个时候(鱼鳞阵)与马其顿方阵或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有什么关系。这或许意味着方阵在康居持续了一个世纪……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马其顿方阵扛着小的圆形盾,这使得人们无法紧密地拥挤在一起,不能出现“像鱼鳞那样排列”。①
结论不成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所建立的大夏在陈汤远征前的一个世纪即已灭亡,而且在塔恩(W.W.Tarn,1869—1957年)博士给德效骞的来信中,说明“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希腊人所拿的小型圆形盾无法使人紧密地站在一起而形成鱼鳞阵势。这样他就改变了之前关于鱼鳞阵来自希腊人的看法。然而塔恩博士在信中提到了公元前54年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士兵,从而让德效骞将鱼鳞阵的运用者重新回到了罗马人。
塔恩教授也亲切地指出,公元前54年克拉苏战败后,奥罗德斯二世 (Orodes Ⅱ)将他的罗马战俘安顿在马尔吉亚那(Margiana)(包括目前的木鹿),以守卫他的前线。一万名战俘有多少人到达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Carrhae)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们在这样的行军中难以得到善待。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娶了蛮夷妇女为妻,并在帕提亚军队中服役。有个故事,公元前36年,安东尼(Antony)在撤退时,得到克拉苏军队的一位幸存者警告和指导。他一直服役于帕提亚。这个故事不真实,叫这人为Mardian的来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但是维勒尤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和弗洛鲁斯(Florus)认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事实或许意义重大。
这些罗马人到达马尔吉亚那后做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他们曾经是军队,靠打仗谋生。希腊人、萨卡(Saca)人和其他人习惯做雇佣兵谋生。
罗马人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罗马国家能够吸收所有罗马人作战。克拉苏的人因遥远的距离和带有敌意的帕提亚人而从罗马领土分离出来了。唯一自然的是,或许这些罗马人中的一些人在机遇到来时,可能会以雇佣兵谋生。
从帕提亚边界、阿姆河(Oxus)上的马尔吉亚那边界到都赖水上的郅 支都城大约有400至500里,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人们像鱼鳞阵一样排列的时间相距有18年。如果这是罗马人的阵势,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有来自克拉苏军队的罗马军团士兵。①
德效骞综合其他学者的说法,认为卡莱战役中战败的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国王安顿在马尔吉亚那,推测他们到马尔吉亚那后会以雇佣兵为生,并认为如果《汉书》中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那么其运用者肯定是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军队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那么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吗?德效骞认为“似乎只有罗马军团的长方形盾的武器和面对弓箭罗马人的锁盾排列能称得上鱼鳞阵”,但罗马人的阵法无法对付中国人强劲的弩箭。
当中国人进入郅支城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首先在远处用弩火箭攻击该镇。任何来自克拉苏军的城外士兵自会像被帕提亚弓箭攻击的时候,很自然地重复地摆出锁盾阵形。没有任何空隙的罗马列队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列队,像一排鱼鳞。力量强大的中国弩箭射穿罗马人的盾牌和盔甲,结果这些人退到城墙后面。②
德效骞还以郅支城的建设来论证罗马军的存在。
罗马人在郅支城的真实存在被中国人发现的城外的双木栅栏(重木城——引者注)③证实。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④
德效骞认为双木栅栏(doublewoodenpalisade)是罗马人军事防御工事的典型特征,由此推断被中国发现的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证明罗马人的存在,郅支单于在建城池时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同时他论证郅支单于还需要罗马人的军事援助。郅支自然需要得到罗马人的雇佣兵。开始时他在康居国王的邀请下来到康居,然而成功驱除可怕的乌孙使他与康居国王决裂,为自己建设一座都城。他的名声让大宛(Ferghana)和其他政权向他进贡,以至于他有钱来雇用雇佣兵。另一方面,他没有大量的匈奴人,以至于他被迫依靠附近地区的人的支持。匈奴人住在现在的蒙古,由郅支的弟弟控制,他将郅支驱逐出来,以致郅支不能从那里得到增援。当他在几个康居贵族和几千驮畜的护送下带军前往康居时,郅支遭遇一场严寒,结果整个队伍中只有三千人完成这次旅程。这样他被迫依靠当地人的帮助。当他与康居国王决裂及杀害国王的女儿时,他冒犯许多康居人,因此自然地会向外寻找雇佣兵。罗马人在他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条件下,被这位著名的武士吸引,结果是相互吸引。①
德效骞认为郅支单于在与康居国王关系决裂,拥有大宛等政权进贡钱财以及他的部众因严寒而锐减、得不到匈奴其他部落的支持等情况下,他可以利用获得的钱财来雇用军事力量为己服务,而罗马人在郅支单于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前提下,答应为其服务,由此得出罗马士兵与郅支单于出于相互的需要而彼此吸引,最终走在一起。得出此结论后,德效骞又进一步地论证摆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
又一个问题排列成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我们在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信息必须靠猜想。当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他用马其顿(Macedonia)的作战方式训练当地的年轻人,结果他从印度回来时,他的总督带给他大约3万这样的年轻人。然而亚历山大有不可抵抗的征服者的声誉,反之克拉苏军团可耻地失败。人们自然不会模仿战败的流亡者的装备和作战方法。希腊国王有时也用希腊风格武装他们的国民,但这些王国是希腊人,有希腊将军。罗马的声誉如果在康居被人知道,一定在这个距离罗马帝国遥远的地方大打折扣。而且成功的龟甲阵需要相当多的技术和拥有罗马人的盾牌,我对除了专业士兵之外的任何人能够应用它表示怀疑。郅支在中国人攻击他之前待在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②
德效赛认为鱼鳞阵需要专业的士兵,技术含量高,而郅支单于来到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于是认为当地人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训练,达到运用鱼鳞阵的水平,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那么在郅支之战中,这些罗马士兵有着怎样的遭遇呢?
当城被攻击、郅支的宫殿被烧毁及其头颅被砍掉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陈汤报告总共1518人被处死(可能大部分是匈奴人),145名敌人被活捉,一千多名敌人投降。这些人被(作为奴隶)分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15个国王,他们是中国的附属国,前来起辅助作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名郅支单于的人逃掉。145名俘虏的古怪数字必定是这些罗马雇佣军的数字。中国人想要康居人保持好的印象,因此追随郅支单于的康居本地人可能被允许逃跑,投降的1000多不是康居和罗马的雇佣军。如果这些罗马人没被杀(雇佣军通常能成功地照顾好自己),他们可能被带到新疆,一些人甚至来到中国。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在郅支之战中活捉的145名俘虏是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而这些罗马士兵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那么为什么在陈汤上奏朝廷的报告中没有提起罗马人呢?
不用奇怪,陈汤和甘延寿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中没有提起任何罗马人,他们的报告成为《汉书》记载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的信息来源。只有他们中的几个人;中国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罗马,可能不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正如威尼斯人不相信马可波罗(MarcoPolo)关于中国的报告。而且陈汤写报告和送画是为了讨好中国朝廷,因为他必须为矫诏出兵远征的行为赎罪。关于一个遥远国家和几个战俘的描述无助于原谅这样的罪过。戴闻达教授已经表示郅支单于城的记录来自在该地所作的画。我们如果没有所作的画不会知道关于这个特殊军事阵形的任何事情。而且这个阵形来自这样一幅权威的画的事实证明我们将一个广泛的推论建立在单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②
德效骞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罗马,所以不可能相信罗马人的存在,于是陈汤和甘延寿的报告没有提起罗马人,而陈汤的写信与送画都是为取悦朝廷,为自己矫诏出兵赎罪,于是运用戴闻达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汉书》中关于郅支之战的记载来自画,同时鱼鳞阵这个特殊的军事阵形也来自画的事实证明其结论建立在“鱼鳞阵”这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德效骞断定公元前54年被帕提亚俘虏并迁移到马尔吉亚那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兵在康居,在公元前36年中国人进攻郅支单于都城时,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罗马人在都城的修筑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然而郅支单于的战败彻底 破坏这些痕迹,而罗马人确实与中国人发生战斗并被先进的中国武器打败①。
综上所述,德效骞在这篇文章中,说明在公元前54年于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首先被帕提亚人安置在马尔吉亚那,然后他们以雇佣兵为生,于是势单力薄的郅支单于雇用了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修筑了郅支城;在郅支之战中出现在汉军面前的“鱼鳞阵”不可能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罗马人,同时这种阵形需要严密的纪律、较高的文明和长期的训练,所以《汉书》中鱼鳞阵的运用者不可能是匈奴人和当地人,而是受雇的罗马士兵;这些罗马士兵在郅支之战中被活捉,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于此,我们可以说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说基本形成。可见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提出了罗马军团来华说,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1957年所发表的著作 《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三、德效骞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德效骞在1941年发表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中对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首先他在文中论述作为古代世界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相遇只能出现在中亚地区。
罗马人和中国人是古代世界两股最伟大的军事力量。在罗马人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an world )的时候,处于汉代(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征服他们的世界里所有值得征服的地方。如果来自这两股力量军队的相遇,可能只会出现在中亚,因为罗马的势力远远没有到达地中海的东边,而中国人几乎没有发现去帕米尔(Pamirs )以西地区的价值。这样的相遇没被注意,因为我们唯一的证据是1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单个奇怪的短语。②
德效骞认为中罗军队只能在中亚相遇的原因在于罗马人在地中海以西活动,而中国人则一般在帕米尔高原以东活动,而中罗军队在中亚的相遇以前未被世人注意,主要在于其证据只是公元1世纪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奇怪短语即“鱼鳞阵”。中罗军队的首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远征康居,进攻匈奴郅支单于的事件。
这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中国西部前沿地区(新疆)的都护做的一个事实,在他自己的职责下,一次到康居(Sogdiana )的远征取走匈奴 (Hun)郅支单于的头颅。匈奴人占领现在的蒙古(Mongolia )。匈奴王位(匈奴皇帝被称为单于)的一个竞争者,他的部落名是Luan-ti,名字是呼屠吾斯(Hu-t'u-wu-szu),统治头衔是郅支骨都侯(Chih-chihku-tu-hou),因此他一般称为郅支单于,杀死一名中国使臣,逃入西方,他被康居国王邀请前往那里,赶走入侵的游牧民族。在显耀功绩的助长下,郅支单于梦想在中亚建立一个帝国,在都赖水(怛逻斯河,Talas)边建立自己的都城,从周边部落获得贡品,一些部落也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中国的副都护陈汤看到这股新力量对中国利益的潜在危险。他集合驻扎在中国西域的军队,在当地政权的辅助下,说服他的上司随征,并出发。
军队成功地走了1000里的长途行程抵达郅支都城,在这里他们立即攻击并占领该城。这次杰出功绩的记载,最近由戴闻达博士数次提及。他表示中国人的西汉历史,我们的唯一原始资料,其信息大量来自一些被陈汤呈送给帝国朝廷的战争画。在此记录中有不同一般的评论,在攻击开始时,郅支城外有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在门的两侧。这个奇怪评论的事实来自一幅画的描述,这给它以不同寻常的可靠性。①
郅支单于在杀害汉朝使臣后,受康居国王邀请,来到康居赶走入侵康居的少数民族,在都赖水旁建立都城,其势力在中亚逐渐兴起。陈汤看到郅支单于的威胁,便集结军队远征,攻击郅支单于并占领该都城。德效骞运用戴闻达关于《汉书》对此次事件的记载来自陈汤呈送给朝廷的画的研究成果,认为100多名步兵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事实由于来自一幅画的描述,因而是可靠的。那么鱼鳞阵来自何处?
鱼鳞阵不是一种简单完成的策略。这些士兵必须挤在一起重叠他们的盾牌。这种策略需要整个群体的一致行动,特别是面对攻击的时候,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发现只有在一支专业军队中应用。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士兵据记载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以混乱的人群冲入战场。
马其顿步兵盾牌圆而小(直径只有1.5英尺),所以无法重叠它们,反之罗马军团拿着大的长方形盾牌,容易连在一起,组成一个保护层抵挡飞弹。然后我们必须寻找某种罗马人能在队列前形成类似鱼鳞的战术以及寻找位于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②
鱼鳞阵是一种复杂的阵形,需要集体的一致行动和高度的纪律性,只能在专业军队中运用,德效骞认为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军队只能是罗马和希腊,于是对希腊和罗马人的盾牌进行了比较,得出:因希腊人的盾牌圆而小,无法摆出鱼鳞阵;而罗马人的盾牌是长方形,容易拼在一起形成鱼鳞状的保护层。于是他认为鱼鳞阵来自罗马而非希腊。那么出现在中亚腹地的鱼鳞阵是罗马人提供的吗?于是他开始在中亚腹地寻找罗马军团的踪影,而在当时能够出现在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可能只有在公元前54年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旧部。于是他对卡莱战役进行描述。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带领7个军团进军帕提亚,其中4000骑兵以及同等数量的轻装士兵。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包围罗马人,整天不断发射致命的箭。罗马军团无用,因为帕提亚骑兵在他们冲锋之前撤退,结果罗马人不能抓住他们的对手。在克拉苏儿子普布利乌斯(Publius)指挥下的辅助骑兵和一些军团发动的一次决定性的冲锋,使这股力量与主力分开。为了防御帕提亚的箭,军团只能组成一个方形,环绕以锁盾。
最著名的罗马阵形是龟甲阵(testudo),在此阵中盾牌锁在一起,在城墙下开展军事行动时,用锁在一起的盾牌放在士兵头上以保护他们。似乎没有记载在这种阵形中罗马士兵也在边上锁盾。在图拉真(Trajan,98—117)纪念碑中发现的龟甲阵样式,罗马军团不仅头上有锁盾而且他们的左边也有。前进时可能难以在右边和前面锁盾,但是当站着不动时,易于形成方形锁盾。然后克拉苏军团的锁盾行动是龟甲阵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把锁盾放在头上,因为普鲁塔克(Plutarch)的原始材料陈述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的人在与主力被切断时,退到一座沙丘并锁盾,但那些人在高于沙丘处,从高于盾牌处发射,因此他们被帕提亚人射中。18年后,安东尼(Antony)的人改进他们的战术,当同样遭到帕提亚骑兵射手攻击时,前排屈膝,将盾牌放在地上,保护后面人的脚,第二排将他们的盾牌举到头的位置,其余人将盾牌举在头上,这样完成龟甲阵。用这种方法,整个军队免受帕提亚的箭,安东尼的人安全撤出。然而,克拉苏的人只是组成单边的锁盾,帕提亚人以高过外面士兵的头的轨道射箭,在自己免受危险的情况下消耗罗马的力量。
在锁盾以抵挡箭方面,希腊人和几乎其他每个人用的圆形或椭圆形盾牌是无用的,只有罗马人的长形盾是有效的,长形盾在外形上是长方形 (形状上为半圆柱形)。一排罗马长形盾在沿着前排步兵延伸得没有间隙,对于之前从未见过此种排列的人而言,看上去像鱼鳞阵,特别是因为它们的圆形表面。否则确实难以描述。
卡莱战役对罗马人是严重的灾难。在随克拉苏出发的42000人中,几乎不到1/4的人逃出。2万人被杀和1万人被俘。帕提亚人押送这些罗马囚犯去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处中亚包括现在的木鹿)去守卫他们的东部前线。1万人中有多少人到达该地,我们不知道,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在这样的征途中难以得到善待。罗马和希腊记载实际上没有关于这些人的进一步报道。贺拉斯(Horace)猜想这些罗马人与野蛮的女人结婚,在帕提亚的军队中服务。①
帕提亚的军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利用罗马军团龟甲阵的弱点,用弓箭射杀罗马士兵,并最终在卡莱战役中获胜。他们将被俘的1万名罗马囚犯押往马尔吉亚那,为其守卫东部边界。那么这些罗马战俘是怎么和郅支单于产生关系的呢?
帕提亚边界、阿姆河边的马尔吉亚那到都赖水边的郅支单于都城大约500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人在郅支城前排成鱼鳞阵时隔18年。这些罗马军团习惯于以专业士兵谋生,希望成为雇佣兵。当郅支单于在康居国王邀请下来到康居时,由康居贵族和几千驼畜护送,骑兵遇到严寒灾害,以致全部人马只有3000人度过旅程。后来郅支单于因军事成功而自满,与康居国王决裂,杀死自己的一个妻子、国王的女儿,修建自己的都城。他不能希望从匈奴获得支持——他们归于正统的单于统治,该单于是他的敌人和半个兄弟,得到中国人的支持。郅支单于由于其专横的行为也与许多康居人敌对。因此他自然会从匈奴和康居疆域之外寻找雇佣军。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白刃战战士,他们因他答应成为痛恨的帕提亚人为敌而受到著名武士的吸引。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域经郅支都城到马尔吉安那的安提阿,所以郅支崛起和他需要军队的消息自然传到罗马流亡者之中。②
德效骞认为在马尔吉亚那的罗马战俘习惯了职业兵的生活,希望成为雇佣军,而郅支单于也需要得到雇佣军的支持,因为郅支单于受康居国王之邀来康居的途中,遭遇严寒灾害而势力大减,后来又因居功自傲而与康居国王关系破裂,同时因争王位而得不到匈奴的支持。势单力孤、处境艰难的郅支单于需要雇佣军,而罗马士兵想以雇佣兵为生,于是相互吸引,在得到郅支单于关于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承诺后,他们成为位于康居的郅支单于雇佣军。德效骞认为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士兵是成为郅支单于雇佣军的克拉苏罗马军团。
在蒙古的匈奴人和帕提亚人一样,战斗时是骑兵射手,然而中国人改进弓,使用弩。一些中国古代的弩如此结实以致要拉开它们需要一个强壮的人背着地,用脚推弓,用手拉弦,这样使用他的脚、背和手臂肌肉的力量。为了控制这些弩,中国人发明不同寻常有效的扳机装置。这些弩是精密的武器,射程比任何其他军队的任何自动武器都远。它们无疑能穿透任何盾牌和盔甲。在进攻郅支城时,中国人自然开始时用一阵弩箭攻击,而他们自己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
以这种方法,中国人甚至射伤郅支单于自己的鼻子,当时他在城内的塔上向进攻者射击。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列被中国艺术家在郅支城外画出,几乎肯定是克拉苏军团的一些人,他们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被中国弩箭进攻时,他们自然重复克拉苏军队在卡莱的战术。除了拿着长形盾的罗马军团,其他士兵和武器无法产生鱼鳞阵的效果。①
德效骞认为中国的弩很厉害,能够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射箭伤敌,在中国军队发射弩箭时,罗马雇佣军重复卡莱战役的战术,摆成鱼鳞阵形。除了鱼鳞阵外,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罗马士兵的存在。
罗马人在此地的存在由双木栅栏得到确认,中国人发现城外有双木栅栏。塔恩博士(W.W.Tarn)说:“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 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被中国人在攻城时烧毁的双木栅栏可能保护郅支城外壕沟上的桥。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只在北部的蒙古由中国人的叛徒修建少数城镇,在康居郅支单于自然想要他所能发现的最好的军事工程援助,罗马军团能在筑城上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②
德效骞认为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可以证明罗马士兵的存在,并且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自身无法修筑城池,郅支城的修建得到罗马军团的帮助。
这些罗马人发生了什么?中国记载陈述当攻城时这些步兵退到城墙后。无疑他们发现中国的弩箭比在卡莱的帕提亚弓箭更有破坏性。中国记录说对于他们没有专门的更多东西。中国人的弩能从城墙上驱赶防御者,结果中国人毫不费力地横扫该城。他们烧毁郅支单于的官殿,取了他的人头,恢复死亡的中国使臣的信用。陈汤报告他处决1518人,这些人可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希望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远征的安全返回。他陈述,另外有145名敌人生俘,1000多人投降。这些人(作为奴隶)被分给西域15个政权的国王,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辅助参加远征。
145名生俘的古怪数字与列队在城外的罗马人的数字(100多)相符合。认为他们与罗马人一致有吸引力。雇佣军通常能在紧急情况下照顾好自己。因此我们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可能仍向东走,去新疆的一些政权。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进一步消息,虽然如果有人去中国很有趣,但是这样的事件似乎几乎不可能。①
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在战役中受中国弩箭的强有力攻击而不得不败退,德效骞认为他们被生俘,因为《汉书》中记载的生俘的数字(145)与在城外摆鱼鳞阵的罗马士兵数字(100多)相符合,并且推断这些罗马军团继续往东走,被作为奴隶,分给了新疆的一些政权,同时认为这些人去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
最后他总结全文,认为中国人在郅支单于的都城遇见克拉苏的罗马军团,而这些罗马士兵从帕提亚人的手中逃出,并在郅支单于的帐下当雇佣军,帮助郅支单于修筑都城;在郅支之战中,罗马军团因其人数少和中国武器先进而被俘,并被带到新疆②。
将这篇文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古》))与前文 (《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公》文)作比较,它们的内容大致一致,但又有一些区别。《公》文明显比《古》文要长,绝不是《古》文的简要版,而《古》文对《公》文在某些方面有所补充。比如补充郅支单于邀请罗马军团兵筑城的原因③,再如补充中国对俘虏的处置,德效骞认为处决1518人可能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想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安全地凯旋;145名生虏(罗马人)和1000多名降虏被分给帮助中国人远征的西域15个王做奴隶,因此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兵进一步向东方迁徙,被送到中国新疆的某个政权。但《古》文基本否定《公》文中关于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④。在结语中,不同于《公》文,德效骞提出即使在公元前1世纪,欧亚大陆间的旅行存在巨大可能性,民族间的影响也难以限制①。
四、德效骞的《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
1943年,德效骞在学术刊物《古典语言学》(ClassicalPhilology)上发表《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一文,主要是为前面两篇文章提出佐证,证明罗马与中国之间在公元前36年发生过一次军事接触,证明《汉书》中所记载的145名生虏是克拉苏罗马军团兵。他在该文中首先对之前的观点予以梳理。
前段时间我提供了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很有可能俘获100多个克拉苏军团士兵的证据。这些人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人俘获的成千上万人之一部分,并且被运送至马尔吉亚那。他们逃跑并且向东朝着中国沿着丝绸之路行走了500英里,来到正由匈奴单于郅支建设的城镇上,他们为其提供援助。一群由中国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助手陈汤领导的中国远征队,侵袭和俘获这个城镇。就目前的讲述,我将提供有关这些罗马人之后历史的证据。②
这段叙述是对德效骞前面两篇文章的总结,简要地讲述了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经过被帕提亚人运到马尔吉亚那,由此逃跑来到郅支单于的都城,并参与此城的建设,在汉军占领该城的战役中再次被俘的经过。至于其被俘之后的情况,德效骞在文中作进一步阐述。
德效骞采用戴闻达的观点,认为陈汤关于郅支之战的报告应包括一系列画,并提出这些画不同于之前的中国画。
这支远征队在许多方面很特别。陈汤关于他的战役的报告包括一系列画描述了对单于城的攻击和俘获——这在之前的中国艺术中是不为人知的。荷兰莱顿大学(LeidenUniversity)的戴闻达(Duyvendak)教授陈述说这些图画包括具有最早记录历史事件的中国绘画作品,其特点复杂,似乎有各种元素得到逐一分析,并形成了一幅混合图画。我相信这在中国艺术中是新出现的。
之前中国画利用的主题是神话、传说以及教化的奇闻逸事。这些是中国画和素描中仅保留和传下来的主题和描述。陈汤的画似乎是中国第一批描绘当代事件的绘画作品。对于朝廷来说,这些作品具有不同寻常之处,因为这些作品展示在每年的新年朝廷宴会上,甚至对于后宫的宫女们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图画。在那次远征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主题,这似乎对中国艺术来说是新东西,刺激这种变化的缘由是什么?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的画反映的是当代事件即攻击和俘获郅支单于的经过,与之前的中国画不一样,因为之前中国画的主题是神话、传说及有教化功能的奇闻逸事,同时陈汤的画还有不同寻常之处,即其在新年朝廷宴会上展示,并吸引了后宫的宫女。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在那次远征中,陈汤取得重大胜利且没有给帝国财政增加任何格外支出,比以前更进一步地将中国军队向西成功地推进,即便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还是为一个中国使者报仇,杀死闻名整个亚洲北部的匈奴武士。为了组织他的远征,他伪造了朝廷诏书,这不仅是死罪,而且拘泥于形式、信奉儒家的大臣对他也有偏见。而且他的上司——都护因拒绝迎娶宦官的姐姐而致命地冒犯了掌权的、控制政府的宦官。因此中央政府最具权力的影响人物都反对陈汤。他明白,除非他以非常生动的方式吸引朝廷对其成功的注意,否则他和甘延寿将受到惩罚。
而且陈汤不是一个自满和骄傲的中国人。他对外国的情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很想向他们学习,具有高超的想象力。他特别善于接受并且非常渴望听到任何新事物。
在这次漫长的返程中或之前,陈汤成功地召集罗马军队的领导,并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说自己的祖国。他们之前的功绩表明他们的领导必然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当时情形下(一个取胜的将军回家),很自然地将罗马凯旋行进的情况(凯旋)告诉陈汤。克拉苏的军队有部分是庞培 (Pompey)的老兵,因此这些罗马人可能目睹或参加公元前60年庞培的伟大凯旋,这仅发生在卡莱战役7年前。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场,他们也肯定从他们的同伴中听说过这一切。
使用画来表现罗马人的凯旋是众所周知的。“孔沿塔代表着被俘的城市,图画和雕塑展现战争的功绩。”在庞培的凯旋中,有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以及与他一同死去的女儿们,以及早于他死去的儿女们的图画。维斯帕先 (Vespasian)与提图斯(Titus)的凯旋中,“战争在各自的部分中由许多手法展现,提供一幅由有趣的事件构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②
德效骞首先从陈汤的处境出发来进行分析,认为陈汤虽然获得巨大胜利,但是其处境异常困难,因为矫诏出征和婚姻问题引起朝中权贵——大臣和宦官的反对,于是,陈汤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处境,必须强调自己的胜利。那么,以何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呢?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高度想象力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采取罗马军团士兵提供的信息,即使用画来表现凯旋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将陈汤的画与凯旋联系起来,这是德效骞听从哥伦比亚大学MosesHadas教授的建议的结果①。德效骞认为《汉书》对郅支之战的描述实际上是九个场景也即九幅画。下面将德效骞所描绘的九个场景与《汉书》中的文字相对照。
德效骞的描述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有少量出入,比如缺少单于在听到汉军前来的消息后,由出逃转为坚守的决策变化过程。《汉书》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①还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德效骞将《汉书》中的“重木城”翻译为“doublewooden palisade”,意思为“双木栅栏”。德效骞认为这九个来自《汉书》的场景与约瑟夫的代表作很相似,是《汉书》中唯一一次对战争的生动记录,而且中国人没有类似凯旋的活动,因而推断班固撰写《汉书》时参考了陈汤的画,陈汤画的灵感来自罗马人的凯旋。这些来自中国历史的场景与约瑟夫(Josephus)对罗马人凯旋的描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这是《汉书》中能找到的唯一一次关于战争的生动记录。班固独自编写他的历史,几乎完全来自朝廷图书馆的文件资源以及档案,可以获得关于战争的书面报告以及图画。中国人除了在胜利军队归来之时设宴庆祝的习俗,没有类似凯旋的实践活动。陈汤这样具有想象力
① 《汉书》,第9册,卷七十,第3014页。
和敏锐眼光的人,在听到罗马人的凯旋以及再现胜仗的各个场景的描述后,他很可能抓住这个特征,将之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元素,生动地描述其不同寻常的胜利以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汤送入中国朝廷的画是如此富有感情,必定来自凯旋中罗马人活动的灵感。如果这个推断被接受了,我们则可以猜测这个画家。从这些场景的特征来看,罗马人可能对这些画的主题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士兵们出现在画中,并非以不合适的方式。中国军队远征随身带着画家和制图者以保留地理和路线记录。然而,罗马指挥官可能选择当地他所熟悉的画家以准备这些场景。佛教信徒的画很可能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或许是在罗马人或陈汤或者其他中国人的建议下,由一位当地的康居人和一个中国人合作完成。①
德效骞认为虽然这些画的主题来自罗马人的指导,但是画的作者不是他们,因为罗马凯旋主要通过舞台造型或人物雕塑来表现,绘画只用于次要的场景,所以推断画的作者是中国人和康居人,他们对罗马人的做法进行了改造,改变了凯旋的表现方式②。
按照上述推理,在郅支之战中被汉军俘获的罗马士兵对陈汤讲述了罗马人庆祝胜利的方式——凯旋以及对陈汤的画造成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陈汤提供了帮助,那么陈汤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那么现在我们对罗马人的最后处置应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陈汤从罗马人获得如此有价值的援助,那么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中国历史对这145个(罗马)步兵毫无记载,仅仅说到这些俘虏被作为战利品(奴隶)分给附属政权的国王,这些国王参加了中国人的远征。而且陈汤的官方报告未提到他的收获,从其他地方,我们得知陈汤觊觎这些战利品,违背法律,在他进入中国之前,拿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该期待我们唯一的来源——历史,提到这些(罗马)俘虏,因为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而中国历史很少有关于奴隶的记载。③
德效骞认为陈汤为了报答罗马士兵所提供的帮助,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虽然《汉书》的记载提到这些俘虏作为战利品被分配给西域的政权,但是德效骞认为中国历史对奴隶不重要,所以关于这些俘虏的下落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史书,因为他认为这些罗马士兵被安置在骊靬县。
然而,我们可以很肯定地陈述这些罗马人的居住地。公元5年,朝廷地籍上列出一个名叫骊靬的城镇。这个名字与中国人用于称呼古代罗马世界的名字一样。在公元9年,中国的王位被王莽篡夺,他开始建立上帝之国,其中所有的名字都与现实相对应。他将骊靬更名为揭虏,两个汉字意味着“抚养贱民(囚犯)”和“攻下城市获得的囚犯(俘虏)”。
中国本土使用外国的地名,在汉朝,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意思——这个中国地方居住着来自国外的居民。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有两个这样命名的例子:现在陕西北部的一座城市与库车的名字相同,在陕西南部一条山脉叫做温宿。库车和温宿都位于新疆。关于这两个中国聚居地,我们特别被告知来自那些外地的居民被安置在这些中国聚居地。然后来自罗马帝国的人们几乎断定在公元5年之前就已经移民到中国,且居住在骊靬。而且,王莽的新名字说明他们是俘虏。①
德效骞认为骊靬是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而汉朝出现了以此为地名的一个城镇,这个地名在王莽建立政权后,为了表示与现实相对应,改名为“揭虏”,强烈地表示着该地的居民为囚犯(俘虏)。同时他以库车和温宿为例来说明汉朝有将外来居民安置在中国,并以该国国名命名定居地的传统。于是骊靬县的出现、骊靬为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王莽将骊靬改名为揭虏的事实以及汉朝以外国国名命名外国移民定居地的传统,成为罗马士兵移民到中国,并定居在骊靬的有力证据。这是德效骞第一次提出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骊靬的观点,此时为1943年。同时他还指出了骊靬县的方位。
古代中国骊靬位于现在永昌南部,永昌城位于甘肃省西面的一条峡谷。该地在公元前121年由中国人从匈奴人手中占领,在那个年代,其居民已经迁移至一个遥远的地方。因此该地逐渐由中国人居住。公元前79年,匈奴侵略该地区,包括骊靬附近的番和。由于骊靬在这个时代没有被提及,或许这个地方还不存在。在公元前35年,当陈汤从康居返回,这个地方很可能有部分无人居住的地区,政府想在此地区殖民,以守卫丝绸之路。到公元5年,该地区有被来自罗马领土的俘虏居住。班固详细记录了中国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除了跟随陈汤的队伍外,没有任何情况能让这么多罗马俘虏进入中国。②
骊靬县位于今永昌县南部,他认为陈汤从康居回来时,该地有部分无人居住区,政府想在此殖民,目的是守卫丝绸之路,于是公元5年被汉朝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此,这也是班固在详细记录公元前1世纪中国历史时没有提及罗马俘虏进入中国的原因所在。
德效骞在文章末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帕提亚人有效地阻止了罗马通往中国之路。任何罗马人能穿越他们的领土的唯一途径是作为战争囚犯的俘虏。位于帕提亚和中国之间的部落只允许小群的商人通过,而阻止任何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的军队护送。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从罗马移民进入中国,唯一能克服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中国西部骊靬的存在很好地证明陈汤确实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以及他把他们带入中国,并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古代中国称呼罗马世界为骊靬的地方。而且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的内容,并且开创后来以画的形式记录战役的惯例,这个惯例起源于罗马的凯旋。①
德效骞认为罗马人进入中国要经过两者之间的帕提亚以及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而帕提亚人不允许罗马人穿越他们的领土,除非作为战俘,同时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也不允许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军队的保护,唯一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他认为骊靬在中国西部的存在能够说明陈汤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并将后者带入中国,安置在骊靬县,而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开创了中国画记录战役的传统。
五、德效骞的《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
德效骞于1957年在《希腊与罗马》(GreeceandRome)杂志上发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这篇文章对其以往关于罗马士兵来中国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德效骞首先依据公元5年出现骊靬地名,肯定地提出罗马人一定移民来到中国,并建立骊靬这个城市。他指出骊靬城在今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
在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和县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用非常古老的中国对罗马称呼来命名的城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他们的城市起外国的名字。在那个清单上,有1500多个城市,只有其他两个城市使用外国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居住着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得出罗马帝国的人一定移民到了中国,并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结论。
这座用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狭长的西北部。在公元前79年不存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是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的时候。也有名字由篡权者王莽命名,他用儒家思想来纠正名字,也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给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座城市他重新命名为揭虏,这个词语包含两层意思:“在占领一个地方时候拿下的胆小鬼【被俘虏】以及‘抚养的胆小鬼’。”然后,是不是中国人抓到一些罗马军团的囚犯,然后将其安置在中国西部边界以保卫边疆?①
德效骞认为公元前79年不存在骊靬城,到公元5年出现,这座城池后被王莽改名为揭虏,于是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抓到罗马军团的囚犯,将其安置在此以保卫边疆?
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有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对罗马充满仇恨,不允许罗马人大量过境,那么这些到中国境内建立骊靬城的罗马人是如何穿越帕提亚帝国的呢?德效骞提出疑问后,开始回到罗马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之中”,并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将欧陆两端联系在一起。他首先从罗马三巨头庞培、恺撒、克拉苏之间的关系讲起,认为克拉苏在三巨头中的优势是经济,而不足确是罗马人最为看重的军事。
公元前60年,在罗马,罗马元老院将凯旋授予庞培(Pompey)将军。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到罗马,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助。恺撒 (Caesar)和克拉苏(Crassus)来帮助他,并形成了第一次三人执政。恺撒在59年成为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在55年也成为执政官。后者后来成了叙利亚总督。
克拉苏对三人执政贡献了大笔资金,这是其他两个人所缺乏的,但是他们的计划所急需的。同时他最缺乏和最想得到的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军事荣耀。他来到叙利亚之后,不顾他最好的将军的建议,向帕提亚人发动战争。公元前54年,他带着42000人进军帕提亚人的领土。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并不断发射一连串致命的箭。骑在马背上的帕提亚人在罗马人上来之前撤退,,越过他们的马匹尾部发射,罗马人陷入无助境地。罗马军团只能形成一个方阵,在四周用锁盾来保护,这样就形成典型的罗马阵形——龟形阵。但是帕提亚人朝罗马人盾牌的上、下方,毫无危险地屠杀了罗马人。到傍晚,20,000人被杀死,10,000人被抓为囚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乘夜逃跑,到达叙利亚。①
克拉苏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出任叙利亚总督后,不听旁人劝告,急切地向帕提亚发动战争。结果,克拉苏打败,罗马军团有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接着德效骞对这些俘虏的下场进行考察。
我们不知道那些囚犯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迁至马尔吉亚那(Margiana),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这是中亚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的梅尔夫(Merv)。这10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的距离超过1500英里,俘虏在这样的行军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好的待遇。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古代诗人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迎娶了蛮夷妇女并服役于帕提亚军队。②
德效骞运用普林尼的说法,认为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安置在马尔吉亚那,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由是罗马人从帕提亚西部来到了东部边界,穿越了帕提亚帝国,为其进一步向东迁徙埋下伏笔。
接着,德效骞开始研究中国方面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中国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一个世纪,现在的蒙古被匈奴人占领,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人。他们的皇帝名叫单于。公元前60年,当他们的单于去世的时候,一场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导致8位请求者将自己立为单于。不久所有的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两个:单于呼韩邪(HU HANS工E)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郅支(JZH-JZH)。当郅支在战争中打败了呼韩邪,后者从中国人中寻求援助,并派他的儿子给中国帝王做随从。中国的惯例是将结盟的外国王子控制在中国朝廷,一方面是作为他父亲良好行为的人质,另一方面是向他灌输中国文化和权力。郅支也派他的儿子来到中国朝廷。呼韩邪很礼貌地请求许可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朝廷,并表示其忠诚。他得到隆重的接待。宣帝很明智地把单于作为客人,并封他为与帝王一样的级别,位于中国人的王和其他高官之上。单于被给予丰厚的礼物,两个月后被护送回内蒙古,在那里他被许可占领某些中国边远要塞。中国人支付高昂的费用以防止给匈奴人入侵中国边界。在这几年中,中国人因为呼韩邪的追随,送给他20000蒲式耳的谷物,这样他就能吸引大量的匈奴来跟从自己。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离开了蒙古,向西走去,试图与乌孙(WU SUN)联合,乌孙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或者吉尔吉斯人(Kirghiz)。然而他们杀死了郅支的大使,并将这个人的人头送到中国。郅支惊人地成功打败了乌孙的军队。但他不能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向北方前进并占领了现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国。1000英里的草原对匈奴来说不是很远,比任何蒙古人以及其他草原骑士都远。
郅支认为在这里他会安全的。他于是向中国朝廷送了一封信,要求归还他那作为人质的儿子。守卫中国宫殿的校尉,谷吉(GUJI )(中国人的姓在前面,如匈牙利一样)负责护送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到达郅支王庭时,匈奴将谷吉和他的随从杀害了。①
他讲述匈奴内部的王位之争,主要讲述呼韩邪与郅支之争。呼韩邪赢得汉朝的支持,处于逆境的郅支被迫离开蒙古,向西迁徙,试图与乌孙联合,但乌孙杀害郅支的使者,并讨好汉朝。在这种情况下,郅支打败乌孙,来到西伯利亚西部。在自认为安全的时候,他要求归还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并杀害汉朝的使者谷吉及其随从,由此与汉朝结仇。为了逃避汉朝的进攻,他又必须向更远的地方迁徙,此时他将迁徙的目的地指向了康居。
因为此时康居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康居(Sogdiana),中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郅支作为一个战士的名声很高,康居国王邀请他住在他的国家东部边界,在那郅支有着比寒冷的北方更肥沃的领土,能够保护康居免受乌孙的攻击。郅支害怕呼韩邪和中国人,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建议,签订了一个条约。康居送了数千骆驼、驴和马。然而在路上,旅行队遭受一场冻灾,只有约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康居。国王对郅支表示欢迎并尊敬地招待,与他结盟,将他的女人送给他做妻子。郅支也将他的女儿送给康居国王。郅支现在深入乌孙国内,杀害乌孙人和让乌孙人成为奴隶,赶走他们的牛羊。乌孙不得不撤退,让他们西部的300英里国土无人居住。
于是郅支变得骄傲,破坏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康居人。他为自己在都赖水(Du-lai river)边建造一座有防御工事的都城。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塔拉斯河(River Talass),它的一条支流消失在锡尔河(Jaxartes)与巴尔喀什湖(LakeBalkash)之间的沙漠中。但是丝绸之路经过塔拉斯河,中国知道这座新城。中国本部西部有一位冠以西域都护头衔的官员,他有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自动化中国军队。当都护受中国皇帝命令出征时,在那个区域的小王国派遣军队予以帮助。①
康居因为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为了自保邀请郅支到康居的东部边界居住。郅支因害怕呼韩邪与汉朝的进攻而接受了邀请。在前往途中,因为冻灾,郅支单于所部遭受巨大伤亡,只有3000人到达康居。康居国王与郅支单于结盟,并互相联姻。郅支单于帮助康居击败乌孙,但因胜而骄,破坏了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了康居国王的女儿及数百名康居人。为了自卫,他修建了都城。郅支单于势力在康居崛起的消息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地传播到西域都护的耳中。而此时的西域都护为甘延寿,副都护为陈汤。德效骞认为陈汤“有进取心,勇敢,有计谋,但是不细心”。在郅支单于势力发展的形势下,陈汤认为这很危险,必须消灭这股势力。他看到郅支单于在中亚发展一个大国的危险。他知道在本地辅助力量的帮助下,都护掌握的中国军队能够打败郅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获得安全保障,那将会太迟了。他的上级甘延寿赞同,但必须首先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远征的命令。然而陈汤指出这样一个请求会带来官方的耽搁,过于节俭的帝国朝廷将认为这样的远征太过昂贵。这时甘延寿病倒。
这对陈汤的诱惑很大。他大胆地伪造一个帝国的命令,要求臣属的政权派遣辅助力量,命令屯田的中国军队前来都护所在地开始远征。当甘延寿的健康好转,他了解到部下的行为,他感到吃惊,要求停止行动。但是事实上危险的行为即假造帝国命令的主要罪行已经犯了,不能够停止。因此在威胁和争论之下,陈汤说服他的上级来接受不灭的荣耀的机会。当一支40000人的力量集结,甘延寿和陈汤派人向东到朝廷送一个文件,谴责自己伪造帝国命令、集结帝国军队的罪过。在同一天,公元前36年的秋天,他们向西出发,前往撤回命令无法抵达的地方。②
西域都护甘延寿病倒的情况下,作为副手的陈汤矫诏出兵远征郅支,结果得到甘延寿的支持。在公元36年,他们分兵两路,穿越乌孙,来到康居,寻求敌视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的支持,并从那获悉郅支单于的情况。
接下来,德效骞开始描述郅支之战的情形。他仍坚持认为《汉书》关于郅支之战的描述来自画,但是将之前认为的九个场景变为了八个,这主要是因为他将之前的第四个场景取消了。德效骞以鱼鳞阵、重木城、图画来证明罗马军团在郅支战役中的存在。认为“‘鱼鳞阵’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如此好的鱼鳞阵势的排列需要高度水平的训练和纪律。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或任何未开化的民族一定完成不了”,在排除希腊人后,提出鱼鳞阵就是罗马的龟甲阵,摆鱼鳞阵的士兵就是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军团;重木城是郅支单于得到罗马人帮助的证据;陈汤报告中的图书说明了罗马人的影响。
他提出史书记载的145名生虏就是摆鱼鳞阵的一百多人,也就是罗马士兵,而且这些人没有投降,只是停止战斗,后跟随陈汤来华,被安置在骊靬县:“当我们将活着的145人的数字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100多的人数相比,我们几乎不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些145名罗马军团没有投降,但只是在他们的雇主被杀后停止战斗。他们可能保持阵形,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人群。他们实际上自由地选择跟随中国人。在中国罗马人相应地安置在一座专门建造的前线城市,对此中国人当然以他们对罗马的称呼——骊靬(Li-jien)命名。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县城名单中,从王莽的命名中暗示居住在此的人是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获得,被抚养,这一切足以证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①这段记述显然将来华罗马军团的处境大大改善了,由之前所述的“战俘”变成了“自由人”。
1957年发表的《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一文综合以上3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但对以前的观点有所补充和修改。该文补充145名生虏被俘时的状态,认为这些罗马军团兵并没有投降,但当他们见到雇主被杀,即停止战斗,很可能仍然保持难以对付的队列阵势。该文修改《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关于罗马战俘去向的观点,肯定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认为他们甚至自由地选择与中国人一起走,在中国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德效骞认为骊靬的郡县名称,以及王莽的命名(将骊靬改名为“揭虏”,暗指该城由攻城战中的俘虏及其后代居住),都足以说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②。
在文章末尾,德效骞得出结论: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百余克拉苏罗马军团兵相遇,并将他们带回中国。中国人使用在任何中国文献中均未发现的词语来描述那次远征中的军事布阵,这种布阵只与罗马军队专用的龟甲阵一致。中国人围攻的匈奴城周围有重木栅栏防御,这种防御方式不为中国人或希腊人所用,却常被罗马人应用。罗马人在取胜后常用图画描述战争中的场景,而在中国却从未有过,但这类图画却成为此次中国人远征报告中的组成部分。更为明显的是在公元前79年至公元5年之间,中国建立一座以中国对罗马的称呼——骊靬命名的城市,这个名称表示该城居民来自罗马帝国。①此外,7世纪时,骊靬人发汉语拼音中没有的“x 音,这也说明罗马的影响②。
1957年出版的单行本著作《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与其论文版基本一致,只是比论文版更为详细,比如详细地解释罗马人自愿选择去中国的原因:“他们逃进周边冷酷的沙漠就意味着饿死,因为他们没有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照顾自己的能力。回到帕提亚同样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是从边防卫所逃走的。中国人则欢迎这些勇敢的战士为其戍边。”③在该书中,德效骞还对骊靬城进行构想,认为它“极有可能是按照罗马的模式建造。罗马军团兵并未向中国人投降,是自由人,所以不可能都听从中国人的规矩。按照惯例,只要他们保持和平,纳税服兵役,中国政府通常听其自然。中国人肯定会派一名朝廷命官来管理该城。因为该城存在几个世纪,他们肯定准许与中国妇女结婚。不管是否有某些殖民因素的影响,该地成为一个罗马人的定居点,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罗马人的殖民地。”④此外,该书与论文版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附录中有中英文对照的《按字母次序的汉字》(“Alphabetic ChineseScript”)表。
六、结语
综上所述,德效骞从1940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57年出版著作,可见他对古罗马军团来华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分析他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德效骞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罗马军团的归宿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战俘的生死难以确定,并认为他们如果未被杀害,最大的可能是去新疆,甚至有些去中国内地;《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断定罗马战俘会照顾好自己,不会被杀害,并推断他们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某个国王做奴隶,被带到新疆,而不太可能去中国内地;《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不再考虑他们的死亡问题,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而是在雇主被杀的情况下停止战斗;强调他们不再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诸王,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向,自愿随中国人走,不是去新疆,而是被安置在为他们特设的汉张掖郡骊靬县。可见,罗马军团的待遇是越来越好,他们来中国时是自愿而非被迫,而且来华后受到礼遇,被安置在专门为他们建造的骊靬城。
(二)罗马军团的战斗力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军团兵被中国的先进武器打败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除强调中国武器先进外,还用数量少来解释罗马军团兵的战败②,《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一反前面战败的提法,称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他们的战阵让西汉联军难以对付,最终是因为雇主死亡而自动停止战斗③。可见德效骞不仅在不断地抬高罗马军团兵的战斗力,还称赞这些罗马军团兵具有良好的雇佣军职业操守。
当然,德效骞某些观点的调整是因为发现新证据,比如在《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中出现西汉设置骊靬县的新证据。这种自己根据新证据不断调整自己学术观点的行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观点的调整可能存有主观臆断的因素,比如受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西方中心观的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过,永昌虽为西北的一座小县城,但作为古骊靬县的所在地,由于德效骞的研究,以及后来者的推动,进一步成为古罗马军团在华的落脚地,因此而备受世人的关注而扬名于外。
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骊靬人起源的DNA鉴定
贾笑天
关于骊靬人的起源,国内外的学者,包括生物科技领域的专家都做了大量工作。前不久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组织团队历时两年,对永昌县有特征的人员进行了采血检验。他们用DHPLC法及其他标准方法从87名骊靬男性标本中,将35个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和12个短串行(STR)基因座从人类Y染色体非重组部分中测定出来,15个单体组织得到确认。单体组织的频率分布情况与附近地区的情形相似。在单体出现频率的基础上进行基础组成分析后(PCA)会发现,地理上相近的人们会群居在一起。但是,多维度分析的结果却呈现出一幅特殊的基因图。更出人意料的是,骊靬人与高加索一土耳其一伊朗人关系非常之近。这也就是说,骊靬人从基因上与西亚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情况源于古罗马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西亚地区。这也与有关古罗马人经常雇用西亚士兵的历史记载相一致。对此我和兰州大学陈正义教授就此进行了主题研究,见研究报告《骊靬人的民族构成》。
骊靬人居住在今天中国甘肃省的永昌县。一些人有着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这些体态特征都与其他的中国人相差很远。这些特征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历史、考古学家和记者的关注。他们推测,骊靬人在与公元前53年卡尔莱 (Carrhae)战役后失踪的一支古罗马军团有关联。骊靬人的起源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最近来自甘肃省的一些报道显示,一支古罗马军团在定居甘肃骊靬村落之前,于公元前36年接受匈奴郅支王的统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霍默(Homer Hasenphlugdubs)于1955年第一次提出:公元前53年,在土耳其南部地区的卡尔莱战役之后,帕提亚人俘获了大约10000名罗马士兵,并带着他们向东行进至乌兹别克斯坦,最后加入了郅支部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骊靬人来说,到达中国并不算困难。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一直以来对霍默的假设批评之声不绝,不过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收集大量的历史材料,接受了骊靬人源于罗马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观点。尽管已经做了许多的研究工作,
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霍默的观点。幸运的是,现代分子生物学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人类染色体非重组部分(NRY)相关联的DNA多态保留了我们标本中的父系基因遗传。这也促进了我们对于男性主导的人口迁移历史的研究。将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Y-SNPs)与Y染色体短串行(Y-STRs)结合起来研究,已经证明是研究骊靬人起源的一种强大工具。学者们据此推测出古罗马士兵可能迁移路线。这条路线起始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卡尔莱,然后向东到达中国,最后定居在甘肃省的永昌县。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Y染色体单体分布分析有关骊靬人基因遗传图中获得基因证据时,有关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数据的研究结果可说明,地理上邻近的人口群居在一起的这一情况,这也有可能是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基因所导致的。大多数已发表的有关,Y染色体变异研究的报告中的观点都有偏颇之嫌,他们赖以研究的系统数据存在失真现象,这有可能是试验人员或者是采集样本过程出现差错所致。
就如在多维度分析中所反映的,骊靬人在基因上与西亚人关系紧密。这一基因上的同质性可以解释为,要么这两种人来自同一起源,要么是两群体间大规模的基因流动,也可能是上述两种现象都有。根据历史记载,大多数罗马军团都是由亚洲雇佣兵组成。所以,骊靬人可能与罗马人没有共同的祖先,而是与西亚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尽管如此,长时间的地理分离也削弱了基因同源的影响。
商业和文化的交往随着基因的流动是符合情理的。自从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西部一直是东亚与西亚人民相会的地方,所以这两个群体间的基因流动也是很自然的事。沿丝绸之路分布的人口也为骊靬人基因库的组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骊靬人在基因上同时也与其他中国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显然,邻近地区群体间的基因流动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骊靬的位置邻近中国其他的民族的聚居区,尤其是中国的汉族聚居区。因此,中国的汉族对骊靬人基因库组成也有一定的贡献。
总之,骊靬人在基因上与西亚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两件发生较早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为西亚与骊靬人之间的联系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一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罗马军团东征及通过丝绸之路的长距离贸易;二是唯利是图的罗马人从西亚向东方移民。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中国人对骊靬人基因构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本文的研究数据取自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
罗马军团、骊靬人民族构成初探
贾笑天 陈正义
一、印欧语系诸民族的形成
(一)印欧语系诸部落的迁移
从西亚、印度到欧洲的广大范围内生活着操印欧语系的各民族。他们是希腊人、意大利人、高卢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伊朗人、印度人等。研究证明,远古时期,印欧语系诸部落繁衍、生息在里海和咸海以北的一片弧形大草原上,该地区位于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广义西域范围内,和现今中国新疆地区相邻。
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印欧共同体开始瓦解,印欧语系诸部落开始向外迁移,其中一支西迁到欧洲,繁衍成希腊人、意大利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支南迁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成伊朗人和印度人。所以,英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斯拉夫人等西方人其实是从西亚即中国人所说的西域地区西迁形成的。
(二)雅利安人和伊朗人
定居在东方的印度和伊朗的部落又称为雅利安人,该词的意思是“高尚的人” 或“贵族”。雅利安人自认为很高贵。德国人等一些欧洲民族认为自己是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后裔,以至于希特勒在雅利安人的旗帜下发动了世界大战。
伊朗人就是雅利安人的转译。国名“伊朗”的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国家。古代的波斯、帕提亚(安息)就是指伊朗。
公元前2000年中期,印度、伊朗人共同体也开始瓦解。一些部落南迁到了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人,另一些部落则留在伊朗高原,成为伊朗人。公元前1000年初,伊朗部落分布到黑海北部地区、西亚和伊朗高原。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和中亚、伊朗、西亚交往密切。
二、西徐亚人和安息人(帕提亚人)
西徐亚人又称斯基泰人,中国古籍称塞人。西徐亚人是游牧民族,强悍英武,出没于欧亚大陆各地,因此,各国古籍经常提及西徐人。他们曾分布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以东,伊犁河流域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周宣王(前827一前781)进攻猃狁(匈奴),迫使他们向中亚阿姆河流域西迁,从而引发了一场民族大迁徙。西迁到中国的猃狁赶跑了当地的马萨格泰人,马萨格泰人西迁到西徐亚人地区,并迫使后者西迁,引发了其他许多民族的大迁徙。西徐亚人曾分布到欧洲南俄草原等地,他们还在波斯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强盛时曾控制了叙利亚,势力范围曾达到埃及边境。
在咸海地区居住的西徐亚人则和达哈人共同生活,后来同化成帕提亚人(安息人)。西徐亚人以游牧为生,幼年时以骑羊为游戏,长大后成为技艺高超的骑士和英武的战士。西徐亚人和亚历山大大帝作战时,采取了沙漠战战术,围绕包抄,飘忽不定,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使亚历山大十分头痛。后来,帕提亚人(安息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术,被称作“帕提亚战术”。帕提亚弓弩手举世闻名。他们练就了好几种绝招,能给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如他们接近敌人时,先让马慢步走,然后慢跑,最后策马狂奔,当接近敌人时,他们快速向敌人队列放箭,同时快速转向,从马臀上扭身向敌人射箭,此种技艺被称作“帕提亚人的回马箭”。帕提亚人使用“帕提亚战术”和“帕提亚人回马箭”击溃了克拉苏和安东尼等著名将领统率的罗马军团。
三、波斯帝国时期(前550一前330年):东西方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从中国孔子时代到公元前1世纪末的罗马共和国后期(中国西汉后期),欧亚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达到新的较高级的阶段。
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Cyrus前558一前529年在位)和孔子(前554一前479)是同时代的人。公元前549年,居鲁士远征中亚,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大夏,阿富汗北部)、索格狄安那(Sogdiana,即粟特,中国称康居)和花剌子模(Aharezm),控制了中亚乌浒河(阿姆河)和药杀水(锡尔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后来,波斯帝国的领土西达爱琴海、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小亚细亚、利比亚、埃及;东至锡尔河、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北达咸海、高加索山脉和里海;南至印度洋、波斯湾。帝国境内有波斯、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为古代文明和东西方民族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
大流士一世(DariusⅠ前548一前486,前521一前486年在位)登基时帝国境内已有许多希腊人,尤其在小亚西亚部的爱奥尼亚省。他率领主要由亚洲人组成的大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征服了欧洲的色雷斯和马其顿,两次远征
雅典,第一次其舰队在圣山的海域被风暴所毁(前492年),第二次在马拉松惨败(前490年)。大流士一世统一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广大地区,生活着欧亚许多民族,国土从喜马拉雅山脚到爱琴海和北非,面积约520万平方公里,约一千万臣民。他的雕像屹立在由30个臣服民族的代表塑像托着的平台上。
波斯皇帝薛西斯一世(XerxesⅠ约生于前519年,前485一前465年在位)经过四年的精心准备,于公元前481年率50余万士兵,战船一千余艘,大举进攻希腊。西方史学之父,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一前430/420年)感叹道:“任何军队都不能和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薛西斯率领着去攻打希腊呢?”
波斯帝国曾长时期、大规模进攻欧洲的希腊等地。这也是波斯帝国境内各种文化、民族和希腊、罗马文化和民族的一次大交流,给人类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希腊雇佣军,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等亚洲各民族的步骑兵是波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也是帝国版图内各种文明和东西方各民族交流和融合时期。
四、亚历山大大帝:要把希腊文明推向全世界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前356一前323年在世)击杀了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波斯帝国灭亡、亚历山大被尊为大帝。
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基本上和波斯帝国相当,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流域和希腊四大板块。帝国只存在了十余年(前336一前323年),但很有特色,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世界影响极大。亚历山大大帝在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一前332年)的教诲下长大成人,他对自己恩师的爱戴超过了对父亲腓力的感情。亚历山大一心要实现恩师的理想:把希腊文化推向东方,建立世界大帝国,实现欧亚各民族的大融合。
亚历山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远征亚洲,决心建立一个版图超过波斯帝国的“世界帝国”,他东征西战,使帝国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和中亚,南至尼罗河第一瀑布。他曾在埃及征兵,率领马其顿等希腊联军进攻波斯等亚洲地区。
为了实现欧亚民族大融合,他以身作则,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他娶的第一位妻子是巴克特里亚(阿富汗)一位部落首领奥斯亚提斯(Oxyates)之女——罗克珊娜(Roxana)。从民族上讲,罗克珊娜出身索格狄安那(粟特,中国称康居)望族。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又娶了波斯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泰娜(Statira)和另一位波斯公主。在亚历山大的授意下,他手下的80名高官娶了波斯贵族的女儿。上行下效,亚历山大的一万多名官兵也和亚洲女子订了婚。他郑重宣布,马其顿人与亚洲女子结婚,可享受免税权。
在同一个日子,亚历山大和手下的高官及一万多名官兵举行了集体婚礼,演绎了欧亚民族大融合的一段历史佳话。因此,亚历山大的一些继承人波斯化或阿富汗化了,如塞琉古王国的创建者塞琉古一世及其后裔。
亚历山大为建立欧亚大帝国而重用亚洲人。前331一前327年,他统治着十二个行省,其中11个省的总督是波斯人,而只有一个省的总督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卫队也由波斯人组成,这引起了希腊贵族的不满。
亚历山大要征服所有的陆地,要建立“世界帝国”,加之亚历山大的老部下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思乡心切,不愿继续远征,亚历山大乘机对军队实行大换血,招收大量的亚洲人入伍,如出征印度时招募了三万伊朗人,后来又征召了三万巴克特里亚(大夏)青年入伍。亚历山大顺应马其顿人的愿望,让他们退伍回国,吸收了大量的亚洲人入伍,后来,他的军队主要由东方人组成。许多马其顿官兵退伍回乡之际,将亚洲妻子和儿女留在服役地,主要原因是怕带着亚洲妻小回老家会和原来的妻子发生矛盾,这样,希腊人在亚洲留下了自己的后裔。
亚历山大曾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撒马尔罕一带和索格狄安那人大战,杀死了十二万康居(索格狄安那)人,攻占了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后来成为康居国的首都。这次惨重的牺牲,在索格狄安那(康居)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同时,亚历山大欣赏康居人的英武,征召大批康居人人伍。
康居和西汉帝国关系密切。陈汤远征匈奴郅支单于时,曾深入康居境内,并和康居军作战。陈汤在康居境内消灭了郅支,引起康居人恐慌,因此,汉成帝时(前32一前7年),康居使者赶到长安,向汉帝国纳贡称臣。康居人会把亚历山大等西方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反之,也会把中国人的信息传递给西方人。
亚历山大大帝开创了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和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希腊化时代。他在征服的领土上建立了70多座亚历山大城,这些城市按希腊模式修建,每座城市中有希腊移民一万多人,许多商人也集中到这些城市,希腊文化由此传播到四面八方。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在阿富汗高原建成四座希腊化城镇,在药杀水(锡尔河)河畔、粟特(康居)、印度、印度河等地修筑了许多亚历山大城。这些城市居住着希腊移民,是希腊化基地。
亚历山大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市(Khud—zhand,曾称列宁纳巴德)修筑了城市,命名为“最远的亚历山大城”。苦盏市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西汉时属大宛国,距现今中国边境三四百公里,西汉时中国军队、使者、商人不断到达这些地区。
古文献记载,亚历山大在阿姆河河谷留下了13500名士兵驻守,仅在阿拉霍西亚Ara—chosia就驻扎了4600名;亚历山大死后有23000名希腊军人定居在伊朗北部和中亚。亚洲人把亚历山大称作伊斯坎德(Iskande),现阿富汗坎大哈
(Kandahar)由亚历山大修建,坎大哈就是伊斯坎德的转音。
在中亚,亚历山大扩张到锡尔河靠近现在中国边境的地方。有人甚至认为,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可能深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英国权威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推测,若亚历山大再长寿一些,他会征服西方及印度,然后在公元前314年奇袭战国时代的中国。
罗马人和亚洲国家交往密切,他们曾派使者拜访过亚历山大,由以上史实推断,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不少有关东方和中国的消息。
五、塞琉古王国(前312一前64年)和希腊化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但希腊化进程继续发展。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为三个主要国家,其创建者都是亚历山大的得力部将,它们都以建国者的名字得名: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希腊的安提柯王国和亚洲的塞琉古王国。三国中塞琉古最大,版图包括原亚历山大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它西至爱琴海,东到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和后来中国西汉的势力范围相重叠。帕提亚(安息)王国和希腊一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王国也曾属塞琉古王国。
塞琉古王国的创建者是塞琉古(Seleucus,约前358一前280年),称塞琉古一世(前305一前280)。他把国都定在当时叙利亚北部的安条克(Antioch,现土耳其Antakya安塔吉亚)。中国史籍称该王国为条支,可能是其国都安条克的转音。塞琉古是希腊人,其王后是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大贵族斯皮特美尼斯的爱女阿帕姆,所以塞琉古王朝也被称作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朝。塞琉古王国继续推动希腊化进程。原是希腊人的塞琉古一世及其继承者为了巩固政权,积极实施将希腊等欧洲人移居亚洲并与亚洲人共融的计划。他们继承亚历山大的计划,也在境内修筑了几十座希腊城市,按希腊方式实行自治,每个城市相当于一个小共和国,是传播希腊文化和欧亚民族融合的基地。
从塞琉古独立出来的帕提亚王国(安息)也深受希腊化影响。塞琉古王国的东部分离出希腊—巴克特里亚(大夏,即阿富汗北部)王国,统治者是希腊人,疆域达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东西方文化、民族在此交会、融合,对印度、中亚、中国等国家影响极大。张骞所到的大夏就是这样深受希腊化影响的国家,这里生息着相当数量的希腊人等欧洲人及其后裔。汉民族通过大夏应该知道许多有关希腊和罗马等国的信息。
六、罗马和塞琉古王国的战争
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实行扩张政策,获得成功。他和托勒密王国进行战争于前198年夺得巴勒斯坦、科埃莱—叙利亚等地。他乘胜渡海攻入欧
洲,占领了色雷斯等地(色雷斯在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之北,位于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希腊境内)。
他重建著名的莱西马基亚城,并向此大量移民,以便控制色雷斯。他进而和罗马争夺希腊等地。一些希腊城邦向他臣服,但另一些城邦不甘受他的控制,并向罗马求援。罗马也早就想控制希腊。因此,双方兵戎相见。
公元前192年,罗马和塞琉古王国发生战争(又称叙利亚战争),次年,罗马击溃了安条克三世的军队,将塞琉古势力逐出希腊。
公元前189年,在马格尼西亚决战中,西庇阿率领罗马军队,再次大败安条克三世的军队。次年,双方签订和约,安条克放弃了小亚细亚和色雷斯,塞琉古王国从此失去了地中海强国的地位,罗马进入西亚,在小亚细亚建立行省。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国被庞培所灭。
从上述罗马和塞琉古的战争,人们可窥视欧亚民族交流、融合的概况。罗马、塞琉古两国的臣民几乎包括欧亚所有民族,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欧亚民族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七、从米特拉达梯战争看欧亚民族交流
(一)本都和罗马的冲突
本都位于黑海南岸的土耳其西北部地区,是一个希腊化国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为争夺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霸权同罗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史称“米特拉达梯战争”。
米特拉达梯家族传说是波斯阿黑美尼德王室的后裔,具有波斯(伊朗)血统。前121或前120年米特拉达梯之父米特拉达梯五世在宫廷阴谋中丧命,年仅11岁的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idateⅥ前132或前131年出生,前121/120—前63年在位)继位,由其母拉奥季卡摄政,但她专横跋扈,竟想谋杀亲生儿子。米特拉达梯六世被迫隐匿山林,历尽艰险。公元前115年,米特拉达梯复位,残酷报复,将其母杀害。
米特拉达梯崇拜亚历山大大帝,梦想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他继承其父的扩张政策,吞并了东邻小亚美尼亚、黑海东岸的科尔基斯(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境内)。此时,黑海北岸的希腊人受到斯基泰人的威胁,向本都求援。米特拉达梯出兵克里木(现属乌克兰),击溃斯基泰人,使黑海北岸希腊化城市和博斯波鲁斯王国(现黑海东北岸和亚速海东岸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带)归顺本都。米特拉达梯又在黑海西北岸现乌克兰、摩尔多瓦、罗马一带扩展影响,同此地区的萨尔马特人、斯基泰人、色雷斯人等部落结成联盟。这样,本都几乎控制了环黑海周边地区。
米特拉达梯五世去世后,本都因内乱几乎丧失了小亚细亚的所有属地。本都东邻小亚美尼亚和西边的加拉提亚、帕弗拉哥尼亚都脱离了本都,成为独立国;弗里
基亚并入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原帕加马王国)。当时,罗马在西亚除亚细亚行省外还有西里西亚行省(两省都在土耳其境内)。罗马势力在小亚细亚不断膨胀,当地的大、小王国都被罗马控制。
为争夺卡巴多西亚(在土耳其中部)对抗罗马,米特拉达梯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亚美尼亚国王提格累尼斯二世。公元前93年,本都王指使自己的女婿亚美尼亚王出兵卡巴多西亚;罗马则指令西里西亚行省总督苏拉干预。苏拉(Sulla公元前138—前78)是罗马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后成为罗马独裁官,大权独揽。他遵照罗马指令,迅速击溃亚美尼亚军队,兵临幼发拉底河畔,这是罗马军团首次进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二)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本都和罗马在今土耳其等地争夺激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89—前84)。当时,罗马在小亚细亚有步兵十二万人,骑兵一万二千人,其中罗马军团占小部分,大多数是从当地征集的同盟者军队。罗马盟国俾泰尼亚(黑海南岸,在土尔其西北部)国王尼科美德斯三世有五万步兵和六千骑兵。米特拉达梯六世有由各民族组成的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四万,另有其子阿卡提阿斯指挥的小亚美尼亚骑兵一万人,以及战车等军事装备。本都还调动了四百艘战舰。
数量占优势的本都军很快击败了罗马和俾泰尼亚联军,罗马军队节节败退。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居民把本都王视为“解放者”,许多城市的居民逮捕了罗马长官,打开城门欢迎本都军队。小亚细亚除西南一隅之外都落入米特拉达梯之手。
本都王向各城市下达密令,屠杀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据史料记载,被杀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达八万人之多,由此可看出当时欧亚各地各民族杂居的大致情况。
米特拉达梯把国都从锡诺普(位于今土耳其北部,黑海海滨的城市)迁至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滨的帕加马(Pergamum,今曼尼萨Manisa)。本都军队渡过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经色雷斯进入马其顿,希腊除伊庇鲁斯外,都处在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控制下。到前87年,罗马几乎丧失了所有东方属地。
公元前87年,苏拉率罗马军队反攻,击败了本都军队,夺回了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又倒向了罗马。前85年,米特拉达梯和苏拉缔结和约,本都接受了罗马的一切条件:退出战争中征服的一切地方,交出舰队;赔款3000塔兰特[1塔兰特talent=3600美元(1942年)]。
米特拉达梯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依然控制着黑海周围的相当大的地区。公元前83—前82年进行了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在苏拉的干预下双方恢复了和平。
(三)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74—前63年)
米特拉达梯六世镇压了博斯波鲁斯起义,扩军备战,按罗马方式改组军队,从“野蛮人”部落中招募大批士兵,建成有十四万步兵和一万六千骑兵的大军。他寻求反
罗马同盟者、和罗马西班牙总督及地中海海盗建立了关系,打算东西夹击罗马。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74—前63年)的导火线是俾泰尼亚(位于黑海南岸,土耳其西北部)问题。俾泰尼亚是罗马忠实的盟国,其国王尼科美德斯三世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王国赠送给罗马。俾泰尼亚和本都相邻,米特拉达梯怕罗马因得到俾泰尼亚而实力大增,危及本都的安全,以俾泰尼亚王位继承者保护人的名义向罗马宣战,击败了罗马人,占领了俾泰尼亚。本都人又攻入和俾泰尼亚相邻的罗马亚细亚行省,几乎占领了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沿岸。但是,罗马统帅卢库卢斯迅速扭转了战局、收复了失地、夺回了俾泰尼亚,攻入本都。
米特拉达梯逃到亚美尼亚,向自己的女婿提格累尼斯二世求援。亚美尼亚王支援本都王,导致罗马军队进入亚美尼亚,并击败了亚美尼亚军队。但罗马军队也出了问题,士兵们对征途艰险和军纪严苛极为不满,几乎哗变。卢库卢斯不敢继续攻击敌人、扩大战果。关键时刻,罗马民主派上台,罢免了卢库卢斯的司令官职务。米特拉达梯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施反攻,回到了本都。
公元前66年,罗马任命庞培为司令官,指挥米特拉达梯战争。庞培攻入本都,本都王主动后撤,庞培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追上了本都军并将其击溃。本都王率残部仓皇逃入亚美尼亚,其女婿提格累尼斯二世见势不妙,拒绝接纳自己的岳父。米特拉达梯狼狈逃入黑海东北岸的博斯波鲁斯王国(在今俄罗斯境内)。本都王的儿子掌控着博斯波鲁斯王国政权,他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和罗马结盟。
米特拉达梯到博斯波鲁斯王国后处决了背叛自己的儿子,夺得了政权。米特拉达梯制订了一个宏伟的战略计划:联络黑海北岸、多瑙河流域、高加索各部落,组成联军,沿欧洲内陆远征,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攻入意大利。为实现此计划,米特拉达梯对占领区居民搜刮勒索,横征暴敛,引起了克里木半岛(现属乌克兰)、黑海东北岸城市起义。米特拉达梯的儿子法那西斯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
米特拉达梯走投无路,饮恨自杀。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3年,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享年约68岁。米特拉达梯六世的遗体由其子法那西斯交给了庞培。庞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安葬在土耳其锡诺普王室墓地中。
米特拉达梯战争以罗马辉煌的胜利告终。庞培把俾泰尼亚和本都的大部分领土组建成罗马行省,把博斯波鲁斯王国交给米特拉达梯六世之子法那西斯统治,并授予他“罗马人民的朋友和同盟者”的称号,本都国灭亡。
八、庞培在东方的功业
庞培利用米特拉达梯战争,为罗马占领了大片领土,把罗马的统治范围推进到亚洲的幼发拉底河和埃及边界。他消灭了本都国,将其领土变为罗马行省;他消灭
了古老而强大的塞琉古王国,变其领土叙利亚等地为罗马行省。他使罗马控制了巴勒斯坦、伊伯利亚(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等东方国家。他任意更换国王,把忠于罗马的人扶上王位,给他们增加领土,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他恢复一些被征服民族的自由,使他们成为罗马忠实的盟友。把忠于罗马和自己的异族王公权贵列为罗马人的朋友,赏给他们王位、领土和金钱。他任意干涉各国事务,成为东方各国的“王中之王”。他在战略要地和形胜之地修建新城,修复被天灾人祸毁坏的著名建筑。这样,罗马赢得了许多东方民族的同情和支持,积极参与罗马的各种事业。
庞培在亚洲还击败了科尔基伯人、阿尔巴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伊伯利亚人(格鲁吉亚人)等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他还击败了米提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其他东方民族。他直逼埃及边界,使埃及国王恐慌,献给他奇珍异宝,给庞培的全部士兵发放奖金,制作了崭新的军服。埃及国王请庞培出兵埃及,帮助镇压叛乱,但庞培拒绝了,令人费解。
庞培在战争中获得大量的财宝和战利品,他按罗马人的习惯,大赏部下,每个士兵获得大量奖金,军官则按级别翻倍赏赐奖金。
公元前62年,庞培率罗马军队到以弗所,由此登船驶向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受到热烈欢迎。庞培在勃隆度辛遣散了军队,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匆匆赶往罗马,罗马人像过盛大节日一样,夹道欢迎伟大的将军凯旋。元老院把“伟大的”称号授予庞培,从此他被称作“伟大的庞培”。
九、罗马军团的民族构成
从本文所列史料看出,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到西亚和欧洲居住着印欧语系各民族,他们起源于远古时期生活在里海和咸海一带的印欧语系部落。
远古时期的先民,过着以采集和游牧为主的生活,不经意间就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古代先民迁徙的情况不可能留下翔实的文字史料,但我们从考古发现和神话故事中可窥知一二。如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赫克勒斯完成了十二件伟大的功业,他曾到阿富汗一带攻城略地;希腊酒神巴克科斯出生于印度,曾长期在印度和阿富汗生活。可见,远古时期,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人曾返回过他们的古土中亚,反之,有些希腊人的出生地在印度、阿富汗等地,这和历史记载相吻合。
根据亚历山大随军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的记载,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说,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马其顿等希腊联军在阿富汗的乌浒河(锡尔河)流域,途经一个有城墙的小镇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当地的居民讲的是希腊语。他们自称是希腊爱奥尼亚人的后裔,祖先是看管迪狄马著名太阳神神庙的教士家族的布兰契戴。可见远古时期中亚的人到了欧洲,欧洲人则迁到了中亚、阿富汗等地。
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等大小国家的统治者都执着地想建成一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这仅仅是统治阶层野心的反映吗?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从波斯帝国到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五百年里,从中亚到西亚、欧洲、北非的各种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大帝国的版图内。有远见的统治者鼓励和支持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各种文化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接近中国的阿富汗、索格狄安那(康居或粟特)等国人民,由于战争等原因移居到西亚、欧洲等地,而希腊等欧洲居民和西亚人民则迁徙到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并在定居地生息繁衍,世代不息。如原在中亚的土库曼人现在分布在从中亚腹地的沙漠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广大地区,而谁又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土库曼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呢?
罗马共和国起源于罗马城周围的一些部落联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兴盛时期,意大利人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罗马共和国从来没有一个人口占全国绝大多数的统治民族,罗马共和国一直是一个各民族的大联盟。
罗马共和国从罗马周围的弹丸之地发展成地跨欧、亚、非的千年帝国,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占国内人口少数的统治民族怎样巩固政权并不断扩大领土。罗马统治者很高明地不断扩大国家领土的奥秘应该就是以战养战、以老异族人征服新异族人,这样,整个国家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随着雪球的不断滚动,新的雪粒成为雪球的组成部分,随着雪球的滚动,雪球的体积不断增大,外围的雪粒逐渐成为雪球的内层。
由主体少数民族和统治民族组成的罗马军团,联合相邻的异民族攻击相邻的另一些异民族。这种民族战争有时十分惨烈,死人很多。
罗马军团一旦征服了新的异民族,便对他们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让忠于罗马的上层统治者继续统治原领地,让他们实行自治等。逐渐给他们公民权,吸收他们参加罗马军团等,利用新征服的异族,再去讨伐尚未臣服的异民族。罗马人也将激烈反抗的异族人士贬为奴隶。但随着时间的消逝,奴隶成为自由人,成为公民,成为军团战士,成为军官和官员。异族人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和中坚。到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高卢人、斯拉夫人的奴隶参与作战,成为高级将领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皇室成为“蛮族”雇佣军首领的傀儡;有些“蛮族”雇佣军首领干脆将皇帝杀死,由自己取而代之。由此可见“蛮族”在罗马国家的实力和受重用的情况。
史料记载,恺撒在西班牙、高卢等地作战时,经常征召当地居民组成协防军,配合罗马军团作战。恺撒亲自从高卢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等民族中选拔骑兵,条件是各部落出身高贵者和作战勇敢者。恺撒给作战勇敢的高卢、日耳曼等民族的战士赐赏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和财物,使他们从贫寒之家一跃而成为大地主。重赏之
下,必有勇夫,许多刚刚被征服或正在和罗马军团作战民族的优秀青年积极帮助和参加罗马军队。
西班牙提提乌斯两兄弟因忠于罗马和作战勇敢而被提拔为第五军团军事护民官,恺撒曾提名其父任元老院元老。
恺撒执政时改组元老院,将原有的600位元老增加到900人。新增成员有罗马商人、意大利杰出市民、军官和军人,也有人出身于奴隶。罗马贵族看到高卢人的首领们成为元老院元老并参与国家政事时大感惊叹,表示强烈不满,一时间,讽刺的对偶句流行于罗马:“恺撒谆谆善诱高卢人民,然后把他们护进元老院;高卢人脱去他们的裤子,套上元老院议员的外袍宽边。”
罗马人征战之际,在就近向行省招募当地各民族的民众入伍,或组建辅助部队,帮助罗马军团作战。若需海军,则从全国各地调动舰只,各地以地区为单位提供一定数量的舰只,其船员由当地人组成。
庞培长期在亚洲等地作战,他按照罗马习惯在部队所到之处征兵。从米特拉达梯战争可知,庞培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今日的俄罗斯境内、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地作战并补充兵员。史料记载,庞培军中有些军团从罗马殖民区征召人员编成,有些军团由逃亡奴隶和地方协防军组成。
有些地区的部落酋长、国王带着自己的军队主动参战,帮助罗马军团。
克拉苏远征帕提亚之际任叙利亚行省总督。这里是塞琉古王国的中心统治区,再加上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对叙利亚的长期统治,这里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几乎包括当时从阿富汗、印度、西亚到欧洲的一切民族。克拉苏在叙利亚补充了大量兵员。克拉苏远征帕提亚从意大利渡海以及横渡底格里斯河之际,遇到恶劣天气,兵员损失极大,他从西亚地区招收兵员弥补军队损失。由于克拉苏从意大利带来的军队自身构成民族成分复杂,已有了大量西亚战斗人员,加之到达叙利亚的补充兵源及征战帕提亚时由周边地区的征召,可以肯定帕提亚之战罗马军团的主体构成是西亚人种。
罗马军团早期编制较小,每军团仅4500人,后来扩编为6000人。罗马军团早期只配备骑兵300人,直到公元前105年以前,罗马军团的骑兵由罗马公民组成。后来,尤其是历次战争以后,骑兵完全由外籍人员组成,原因之一是罗马人骑术不精,在马上战斗力极差。罗马骑兵以日耳曼、高卢骑兵最为精锐。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骑兵战斗力很强,参战的努米底亚骑兵就多达七千人以上,他们骑马不配缰绳,十分骁勇。骑兵中不乏西亚籍士兵,如高加索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小亚细亚人、伊朗人等。甚至帕提亚(安息)骑兵和弓弩手也参加到罗马内战之中。关于罗马军队的民族构成一来史料零散,二来古代民族十分复杂,如日耳曼人中就
有十余支,十余支名称,本文不便一一列举了。
由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数百年的统治,加上古代的欧亚大陆上战乱不休,欧亚大陆间经常发生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现象。小亚细亚、西亚、高加索、土耳其、伊朗、色雷斯、希腊等地位于西亚到欧洲西端的中心部位,欧亚各民族在上述地区杂居、融合。后来,色雷斯、西亚、高加索、伊朗、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又在罗马共和国版图之内。所以罗马帝国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几乎包括当时欧洲、西亚大陆的所有民族。
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大夏(阿富汗)人、康居人(索格狄安那人)移居到叙利亚、小亚和黑海沿岸。这样罗马军团也有一些伊朗、康居、高加索等地区的血统。但据历史记载,这三大帝国人侵中国的企图都未能实现,如果说有一支罗马军团曾在汉时被安置在河西,并定县名为骊靬之说成立,那么移居到中国的骊靬人的血统更为复杂,现在他们除中华民族各民族的血统外,还应有西亚及意大利血统。
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以基督教约翰王传说为例
姬庆红
约翰王(PresterJohn)是一个12至17世纪期间欧洲教会和诸侯所熟知的名字。他的传说因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的一封署有这个名字的信件而在欧洲风行。该信称约翰王统治的地区物产丰饶、子民和谐,并承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基督教对付敌人。该信件自问世后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先后出现了德、法、英、拉丁等语言的100多个抄本。约翰王及其传说影响深远,甚至在哥伦布以后多年仍能唤起欧洲人的热情。当然,约翰王的传说确有些荒诞不经,但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去考察,便可发现,它反映了中世纪西方人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对美好社会追求的内在价值。一、约翰王及其信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亚洲在欧洲人的印象中只是一张充斥着想象和传说的地图。有关约翰王的传说便是其中之一。最初,欧洲的朝圣者和旅行者把名字及其故事传人欧洲:在遥远的中亚,有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其统治者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长老——约翰·普里斯特,是《圣经》拜见圣婴耶稣的东方三博士的后裔。他在中亚所向披靡,声名显赫,俨然拥有着一座域外的上帝之城。1145年,德国主教奥托在其著作中提到,一位叙利亚主教亲口向他讲述了这位基督教约翰王的故事,说他打算到耶路撒冷与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并肩作战。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署名“约翰王”的信。信中介绍了约翰王的显赫地位、财富及其对基督教的虔诚,引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兴趣。这封信迅速被译成12种以上的欧洲文字,人们争相传抄和阅读。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约翰回了一封,并派遣了曾到过东方的医师菲利普(Philip)作为信使。①
当时,欧洲的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家对约翰王及其王国纷纷进行猜测。一部分人认为约翰王在印度,这可能是把他与传教士圣·托马斯混淆了。另一些人认为约翰王国应位于中亚某个未知地区的中心。上述猜测的依据是这两块地区分布有涅斯托里教派和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组织。不过,到14世纪,大部分欧洲学者已放弃了该王国在亚洲的猜想,而认为它在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王国。到16世纪末时,约翰王出现在荷兰人和德国人绘制的南部或东部非洲地图上。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德国学者为首的国际学术界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迄今不衰。概而言之,关于约翰王及其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约翰王人物原型的研究。约翰王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马可·波罗认为,蒙古草原部落克烈部首领王罕脱里才是真正的约翰王。1322—1328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岛中国旅行,把汪古部的首领当作了约翰王,并指出以往关于约翰王的种种传说不足为信。①研究该问题的先驱学者古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和弗雷德里希·赞克(FriedrichZarncke)认为,约翰王就是中亚Qara-Khitay帝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②鲁布鲁克认为,约翰王是指乃蛮部的屈出律。俄国学者布鲁恩(Ph.Bruun)于1976年提出,约翰王应在格鲁吉亚中寻找,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格鲁吉亚正在经历对穆斯林势力形成挑战的军事复兴。③M.巴伊兰(M.Bar-Ilan)则认为,约翰王信中的约翰居住在印度,而不是埃塞俄比亚。④1923年,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马里涅斯库(ConstantineMarinescu)认为约翰王的原型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1931年,意大利学者李奥纳多·奥勒斯吉(LeonardoOlschki)另辟蹊径,首先提出约翰王传说只是乌托邦。他相信,约翰王及其信件并没有历史原型,根据地理寻找他的王国毫无用处。此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如有人认为这个传说是混合了某些放纵诗人与朋友取乐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当代研究者已经放弃了固执一说的做法,而更注重对该传说历史演变的考察,例如大卫·摩尔根(DavidMorgan)考察了13世纪期间约翰王“候选人”的变化过程。⑤
第二,关于约翰王传说缘起的研究。关于该传说产生的根源,学术界的观点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寻找基督教盟友。约翰·拉纳(JohnLarner)认为,约翰王的传说表达了西方人寻找对付穆斯林的天然联盟的一种强烈愿望。①中国学者吴莉苇也认为,十字军东征时期凡有远东的军队攻打穆斯林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涉及的地理区域都被编入约翰王的故事中,那些穆斯林的敌人们就被基督徒设想为约翰王及其臣民。②瓦西里耶夫(A.A.Vasiliev)也指出,约翰王的信件于14或15世纪在俄罗斯流行也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盟友,以消除鞑靼人的威胁。③ 第二,欧洲神权与世俗权力之争的需要。例如,汉密尔顿认为,该信件是德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Barbarossa)差人伪造的,是他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斗争期间宣传的组成部分。④
第三,借以改善欧洲基督教社会道德状况。李奥纳多·奥勒斯吉认为,欧洲人虚构约翰王的目的是表达对当时欧洲基督教分裂状况的讽刺,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其目的在于改善欧洲人已经败坏的社会道德。⑤ 第三,该信件作者身份的研究。由于该信件出现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人认为约翰王“部分上是十字军想象世界的一个产物”,即此信作者应为基督教会的教士。李奥纳多·奥勒斯吉也认为其作者是西方教会的一个牧师,但他在信中只是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M.巴伊兰认为约翰王之信的作者是中世纪意大利的犹太人。⑥伯纳德·汉米尔顿(BernardHamilton)将其视为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为政治目的伪造品,可能由费雷德里克国王的大法官,科隆的大主教莱纳德·冯·达赛尔(Rainaldvon Dassel)炮制而成。⑦国内的龚缨晏先生运用中国古籍与国外学者长期研究成果相对照,对各种观点给予了评述,但并未表示支持其中的一种。⑧
二、中世纪西方对约翰王的“寻觅”
(一)雾里看花:11~12世纪,印度神奇的约翰王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西方的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为了巩固和扩大天主教的势力,极力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地中海东岸国家和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企图建立“世界教会”。然而,阿拉伯国家此时势力已经壮大起来,并对西方世界构成强大的威胁。尤其是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SeljuqTurks)占领了耶路撒冷,对教皇和基督教世界打击很大。欧洲人渴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但是多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成果,加之罗马教皇与欧洲各君主争权夺利,使整个欧洲社会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
于是,他们开始寄希望于在穆斯林世界的东面能有同盟者,约翰王的故事也就不胫而走。约翰王的原型可追溯到《新约》中的“约翰王”的提法。①在传入欧洲之前,约翰王的故事也许在亚洲的聂思脱里教派中流传已久。1122年,一名自称来自印度主教约翰(PatriarchJohn)到达罗马,要求教皇承认他的职位。这名主教约翰声称,自己所在的胡尔南(Hulna)城建在婆黑森(Phison)河边,规模和势力很大,虔诚的基督徒居住其中。城市外,十二僧侣为了纪念十二圣徒修建了圣托马斯大教堂,在他的斋戒日全亚洲的基督徒都来参观。②对此,约翰·拉纳表示:“我们面对的不过是某个自信的骗子,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制造出把戏糊弄教皇。”③ 但是,这个在东方影响力很大的基督教团体的故事还是被传播开来。
最早一份关于约翰王的记载见于德国弗赖辛(Freising)的奥托主教(BishopOtto)1145年发表的《编年史》。奥托声称亲自见到来自安条克公国的主教休(BishopHugh)向罗马教皇尤金三世(PopeEugeniusⅢ)报告说,在世界的最东方,有一名国王兼长老的约翰,是基督教徒,是《圣经》中的古代东方三博士④的直系后裔,曾打败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穆斯林国王塞米阿第(Samiardi)兄弟,并攻占了其都城埃克巴塔那(Ekbatana)。他受到祖先的激励,想到圣城耶路撒冷朝拜,但因军队无法穿越底格里斯河而退兵。根据学者的研究,休提到的这场战役可能是1141年哈喇契丹(1124—1211年,即西辽帝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Yeh-lüTa-shih,1094—1143年)与塞尔柱苏丹桑贾尔(SultanSanjar)在中亚河中地区卡特万(Oatwan)的会战,结果后者战败导致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这块地区。而耶律大石的突厥语称号“葛儿罕”(汉字又译作“古儿汗”、“菊儿罕”等),读音后讹传为希伯来文的Yohanan或叙利亚文的Yuhanan,由此再转化为拉丁文的Johannes或John。①经学者考证,耶律大石本人并非佛教徒,而是萨满教或后改信佛教徒,因而休提到的约翰王误以为是耶律大石②,但耶律大石统治部落中确有涅斯托教徒。
在1165年,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没有地址的“约翰王之信”。这位约翰王首先声明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城中的基督教徒处处受到保护”,但也有不少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民。其次自己的王国疆域广大,“统治三个印度”,“如果您确想知道我的权限范围的话,那么请您坚信,我,约翰·普里斯特的统治至高无上,其美德超群,我十分富有,统治着天下的万物生灵。” “地上蜂蜜流淌,处处都有牛奶”,“到处有着奇珍异宝”。皇宫金碧辉煌,“采用圣托马斯为King Gundoforus设计的模式建成”,经常用隆重盛大的宴会款待子民。“在这里没有做伪证者、货币伪造者、私通者或强奸者”。最后,讲述国内神奇事物。城内有亚历山大之门(theGateofAlexander)和不老泉,有一个魔镜能够看到自己统治区域的任何角落。
由此来看,约翰王及其传说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是欧洲人在没有使者或传教士亲自到亚洲考察前对东方的想象,其中的“错误”自然难免,例如信中所谓的“三个印度”③,以“近印度”向东最为突出。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印度就是世界的最东方,约翰王就是东方的统治者。这种想象很可能是根据亚洲的聂思脱里教徒或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道听途说的亚洲战事,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军事的失利需要外部帮助的需求下产生并广泛传播的。
(二)犹抱琵琶:13~14世纪,中亚草原上的约翰王
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大军的西征使东西方的碰撞与认知成为可能。随着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顺利进行,基督教徒占领了兄弟国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暴露了罗马教皇积极寻求对已知世界的封建君主的权位争夺,而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在黑海和其他东方地区“发现”了更多的基督教徒,并错误地认为穆斯林世界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超过了穆罕默德的信仰者。这无疑激发了罗马教皇更大的野心,也更加使欧洲人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位皈依基督教的约翰王将会帮助他们取得尘世和精神的巨大胜利。
13世纪初,蒙古人的迅速崛起与对外扩张是西方人始料未及的。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三次西征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对于这个彪悍、野蛮的可怕民族,西方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并企图到他们中去寻找梦寐以求的约翰王。
1221年,随十字军东征至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巴勒斯坦的阿克雷主教(BishopofAcre)德维特里(JacquesdeVitry)和西部教会的佩拉吉斯枢机(Cardinal Pelagius)向罗马报告说:“两个印度的国王”大卫王正率领着彪悍的军队帮助基督教武士们,并吞掉了强大的撒拉逊国。他是约翰王的儿子或孙子。①其实,他们所指的大卫王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因为后者在1219—1222年间攻灭了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花刺子模(Kharezm),并占领了波斯东部的呼罗珊诸地。这让欧洲的基督教徒们群情激昂,更加坚信约翰王的存在,并将之视为攻打穆斯林的天然同盟。
1240年前后,蒙古人的铁蹄踏进欧洲,使欧洲人关于约翰王的美梦变成了歌各和玛各的噩梦。其实,最早意识到蒙古人威胁的是穆斯林异端亦思马因人。他们在1238年曾向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建议结成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大同盟共同对付来自东方的可怕敌人。但是,这一建议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当时西欧教俗权力之争,尤其德皇腓特烈一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根本无暇顾及尚未成为重大威胁的蒙古人;同时蒙古人对穆斯林世界的打击,让欧洲人乐于坐山观虎斗,想渔翁得利,让“全球变得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基督”。
拔都第二次西征,饮马多瑙河,里格尼茨打败西波联军。这使西方世界惊慌失措,各种猜测随之产生。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Paris)满怀恐惧与憎恨地称,蒙古人就是《圣经》中预言的来摧毁基督子民的歌各和玛各的后代,他们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 。他认为,这也许是上帝假鞑靼人之手来惩罚他们的罪过。
与此同时,教皇格里九世呼吁组织十字军抵御蒙古人。但是,由于德皇与罗马教徒互相攻讦而流产。③1245年,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集中讨论如何防止蒙古侵略的问题。一面对防御工作,一面派遣教士充当使者,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戮基督教和侵犯欧洲,并企图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随后,罗马教会和国王纷纷派遣传教士前往寻求约翰王。其中有著名的博朗·嘉宾、阿西林使团、路布鲁克等人出使蒙古,尽管结盟的使命没有完成,但他们得知蒙古人中有不少聂斯托里教徒,使得欧洲人依然坚信在鞑靼人和穆斯林所构成的屏障以外存在约翰王的国度。
在此期间,1241年窝阔台大汗病逝,致使在欧洲征服的王子们抽兵回国,西征暂时停止。此后,蒙古人再也没有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攻势。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噩梦。于是,他们编造出各种说法来描述他们是如何打败和赶走了蒙古人。1253年,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摧毁巴格达和叙利亚,让基督教世界一片喝彩。蒙古人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认为蒙古人是伊斯兰教的天敌,是上帝的意志让穆斯林招致灭顶之灾。但是,蒙古人对待欧洲的反复无常,让他们相信,蒙古人肯定不是他们所期盼的约翰王。
在此背景下,马可·波罗的叙述充当了确认歌各和玛各之地与约翰王之国地理位置的重要角色。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从六十三章至六十七章、七十二至七十三章节中都涉及约翰王的问题。①其大体内容如下:1.鞑靼人确实是居住在北方的玛各人②。但歌各与玛各之地曾被约翰王③所征服,但现在约翰王的国土又被鞑靼人征服。2.可汗宽容那些不反对帝国臣民的各种信仰,因基督教徒战前占卜成吉思汗取胜,故优待基督教徒。3.鞑靼人与约翰王之后联姻,如成吉思汗纳王罕之女为妾,四子拖雷娶一女。而约翰国王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公主为妻。
尽管马可·波罗在该问题认识上出现了不少史实性错误,但他为鞑靼人和约翰王这原本敌对的两族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约翰王也不再是传奇中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被蒙古人打败的真实人物。最关键的是,马可·波罗认为,契丹是鞑靼人统治的约翰王之旧地,并仍有众多基督教徒生活其中。④而且,在契丹南面是居民为偶像教徒的蛮子国。⑤这使得欧洲人对“大印度”之中的“近印度”多了一些具体的知识。但在蒙古帝国瓦解后,欧洲人开始动摇这个念头:约翰王是否确实是中亚大草原上的某个国王。⑥随着13世纪末天主教派来到元朝,聂斯托里派在大草原上的历史逐渐结束,约翰王及其传说也随之淡出亚洲。
(三)蓦然回首:14~18世纪非洲的约翰王国
蒙古作为一个霸权国在亚洲的兴起以及商业在欧亚世界体系中的扩展,西方人开始意识到最遥远的亚洲内地与约翰王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是,欧洲人很快为他在未知的和神秘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个新家。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除了欧洲人对亚洲约翰王的幻想破灭外,埃塞俄比亚从4世纪开始就是一个传统基督教国家。自从约翰王的传说开始,欧洲人就认为他统治着三个印度,但他们对“印度”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模糊的。约翰王之信的作者由于缺乏对印度洋的基本知识,把埃塞俄比亚看作三者之一。当时的西方人就知道埃塞俄比亚很早就是一个基督教民族王国,但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欧洲与它的联系非常少。
其次,认为约翰王应在埃塞俄比亚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宗教认同。在中世纪晚期,耶路撒冷是欧洲与非洲之间三大交流地区之一(其他两个是南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随着十字军控制了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东方基督教文化的净土” 的城市(1099—1189年,1229—1244年),该城市受到各派督教的关注,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派。在这个教派林立的城市,十字军是否可以首次代表着基督教跨越洲际的自我觉醒还在争论之中。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地位代表着不是以种族认同而是以宗教为枢纽对“他者”的认识。①1244年耶路撒冷重新陷落后,埃塞俄比亚被欧洲人处心积虑地继续解释为欧洲以外反穆斯林战略的中心舞台。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要求约翰王重新团结在天主教会的旗帜之下,并在1300年为基督教协定拟订了计划,包括“亲爱的努比亚和上埃及其他国家的黑肤基督徒”。②
最后,还与该时期埃塞俄比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有着直接的关系。13世纪后半期,在十字军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期间,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所谓的所罗门复兴时期——扎格维王朝(Zagwe,1137—1270年)时期。其前几代君王,如耶库努·阿姆拉克(YekunoAmlak)、雅各布·塞容(YagbeSeyon,1285—1294年)等励精图治,壮大了军事实力,并加强了宗教力量,随后在东非高原实行了连续的扩张和巩固政策。强盛时期,扎格维王朝时期,基督教已经战胜了世俗权力,其统治的领域甚至超过了阿克苏姆极盛时期,并重新夺回红海贸易权。
鉴于以上原因,欧洲人在埃塞俄比亚为约翰王安置新家,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1306年,30个埃塞俄比亚大使被皇帝威德姆·阿拉德(WedemArad)派往欧洲打开了双方之间的外交来往。在他们被询问的记录中,提到他们教会的主教叫作约翰。第一个清楚描述非洲长老约翰王的是,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士约旦努斯 (Jordanus)于1329年发表的《趣闻集》中。当讨论“第三个印度”时,他记录了不少非洲大陆和国王们的趣闻逸事,并说欧洲人把他们叫作长老约翰王。③从此,非洲约翰王国的说法流行开来。
1487年和1507年,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互派使者。欧洲人加强了对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直接认识。1520年,埃塞俄比亚皇帝莱伯纳·邓格尔(LebnaDengel)与葡萄牙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这期间,约翰一直被欧洲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名字。有学者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说,埃塞俄比亚的宗教语言和上层语言中“国王”或“陛下” 可以写为Zān、ān或者ān,其发音有些像法语中的“Jean”或者意大利语中的“Gian”,都是指John。埃塞俄比亚的主教就是国王或者Zān。①尽管如此,但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人从未这样称呼自己的皇帝。
当皇帝扎拉·雅各布(ZaraYaqob)的大使于1441年参观佛罗伦萨时,当议会的高级教士坚持说他们的国王就是约翰时,他们感到很疑惑,并试图解释在一系列皇帝的名单中就没有出现过这个称呼或头衔。②然而,他们的警告没有阻止欧洲人继续这样称呼他们的皇帝。此后多年里,埃塞俄比亚都被认为是长老约翰王传说的起源地。欧洲人一厢情愿的做法是因为满足外部基督教盟友的宗教情感的需要。埃塞俄比亚是远印度或近印度,或者是第三个印度,对于欧洲人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它是基督教盟友即可。现代学者在古代资料中找不到约翰王及其国家,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也有说服力地证明,在与欧洲正式接触前,这个传说并不为埃塞俄比亚人所熟知。其实,早在18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曾否定了自己是约翰王或叫约翰的说法。捷克方济各会雷米蒂·普鲁特科(RemediusPrutky)于1751年问及皇帝伊雅苏二世(Iyasu Ⅱ)这个说法时,皇帝很吃惊,并告诉他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从不习惯自己这样被称呼。③这应该是由埃塞俄比亚君主来回答欧洲人这个传说的首次记载。当被想象的“他者”亲自站出来,澄清“自我”的真实身份时,再固执的想象者也该恍然大悟了。此后,这位神奇的约翰王只能脱下历史的外衣,进入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发挥“全能至上”的本领了。④
三、余论
从12世纪至14世纪,欧洲对约翰王的认识经历多个人物原型的变化,对其领地位置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印度到中亚,再到非洲的转换,最后只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个转换历程清晰地反映出西方对东方的认知由模糊状态中的完全想象,到逐渐修正为部分想象,最后到认识清晰下的想象褪色、消失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说,约翰王及其传说是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将东方作为他者,根据自我需求构建东方、臆想东方的结果。但是,约翰王的传说又并非子虚乌有,正如查尔斯·E.诺维尔所说,约翰王的传说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方传说与真实历史事件奇妙的调和物。①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作了长期大量的努力,探讨约翰王(或信件)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结果仍无定论。他们论争的出发点是传说或传闻与“历史事实”不能相容。然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追求绝对真实不同,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事实背后的真相。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待该问题,即是否可以把它看作中世纪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在浪漫化异域的同时,追求一种政治地理的知识,是“幻想地理”和“真实地理”的综合体。②也许约翰信件本身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表达某种观念,或描述某个真实的地理区域,而是让理想世界和现实政治观念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叙述出来。约翰王信件对其王国的描述俨然是人间天堂或上帝之城,充满着美德、正义与和谐,远优于12世纪西方腐败的基督教世界,其实这是基督教的普适主义理想的境界和象征。只不过因现实残酷的宗教斗争,这种对东方异域的浪漫化想象被西方人企图纳入自己斗争的“阵营”当中来,而少了些美好和高尚,多了些世俗和污点。
约翰王无论作为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传说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教会分裂、教俗权力之争以及十字军东征失败的年代,约翰王似乎成为了驱除伊斯兰教的象征并使欧洲人精神上有所寄托。因此,从12世纪直至美洲发现后,这个传说甚至成为欧洲思维模式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作为穆斯林后方的一个潜在的基督教盟友,为后来十字军的行动计划提供了参照,因而在欧洲的世界战略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约翰王的传说引起了欧洲人对未知领域的积极向往,刺激了欧洲君主们对海外探险的兴趣,从而推动了理大发现的到来,因而约翰王的传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几个问题①
丁得天 高倩
刘萨诃,法名释慧达,东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高僧,其事迹在佛教典籍、碑记、石窟壁画、民间信仰和传说中多有记录,广为流传。国内外学术界对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探讨已经持续了近百年的时间,[1]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台湾佛教史学者陈祚龙先生著文开始,又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2]至今仍尚未停息,且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其不仅在佛教信仰、史籍、文物考古、美术史、图像、民族及敦煌等学术领域有热烈的讨论,而且在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亦有全新的探索。诸位前贤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硕,只能望其项背。笔者自不敢班门弄斧,而是因较为熟悉金昌的历史和地理概况,又对圣容寺及番禾瑞像颇感兴趣,对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问题也略有一些思考,囿于所学,故此求教于方家。
一、相关的文献记载
刘萨诃及其事迹,正史和佛典都有收录,材料比较丰富,如南朝王琰的《冥祥记》,梁慧皎《高僧传》,姚思廉《梁书》,唐初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释迦方志》,唐释道世的《法苑珠林》等都列其事迹。刘萨诃,或称萨荷、萨何、萨河、摩诃等。其民族属性在各类典籍中记载是比较一致的,都是稽胡族,是包括匈奴、胡人以及当地土人的“杂胡”。[3]南北朝时活动于今陕北、山西西北部一带的山谷中,以游牧、射猎为业,后逐渐与汉族融合。关于刘萨诃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王琰的《冥祥记》中。王琰仕于齐、梁间,约生于宋孝建元年(454年)前后,幼年受戒成为佛弟子,曾游历于江都、峡表等地,齐建元元年(479年)复还京师。他在《冥祥记》中自称幼年时从贤法师处得到一尊观音金像,此像能“放光照三尺许,金辉映夺”,自得到此像以后,“瑞验之发,多自是兴”,故《冥祥记》一书不免多有离奇荒诞之事,不过其成书时间距后来故事中番禾县望御谷“授记”的时间却是最近的。
《法苑珠林》卷八十六《冥祥记》载: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
《冥祥记》中之事多不可信,自然也包括刘萨诃“暴病而死”、“至七日而苏” 之类冥游、灵验的故事。不过我们从此处还是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对刘萨诃的一些认识:可能是今山西离石(今吕梁地区)人,三十一岁出家。出家之前可能是军卒。不知道有佛法,尚武,尤好田猎。得暴病却未死,七日后苏醒,醒来以后就叙述了一些他在地狱中冥游、受到点化出家、精勤福业等种种不平凡的经历。
这里需要留意刘萨诃出现的时间及其年龄。文中记载刘萨诃出现时的年龄已是三十一岁,也就是其出家时的年龄。据文中所记,出家以后他又在江东、许昌等地游化,游化了多长时间文中没有提及,太元末年(396年)仍知其在京师,由此可以推算刘萨诃至少生于366年,但依照王琰的语气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刘萨诃在江东、许昌游化的时间已不算短,生年要早于366年,再往后其行踪就不知所终了。再看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释慧达一》:
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域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先是简文皇帝于长干寺造三层塔。晋太元十六年(391年),孝武更加为三层。达东西观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厉,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慧皎乃佛教史家,其书历来为佛、史两家所重。《高僧传》中记事截至梁天监十八年(519年),成书时间较《冥祥记》略晚。从上文的记述来看,《高僧传》相较于《冥祥记》的记录更为简单平实,但多出了刘萨诃晋宁康中至京师礼长干寺、拜阿育王塔像等“东西观礼,屡表征验”之事,且刘萨诃“忽如暂死”以后,只用“备见地域苦报”来一笔带过其在地狱冥游时离奇繁复的经历,基本是叙述了刘萨诃在江东一带的活动轨迹,以及因统治者信佛而修造塔寺之类的活动。可见慧皎对这类感通、冥游之类的故事不似王琰那般重视,或者说有意做了精简,就使得可信
的成分增大了。[4]实际上,慧皎和王琰生活的时代相去不远,慧皎既要为高僧立传,必然要取其重点,略其枝节,这也是关于刘萨诃早期的事迹中相对最为可信的记录。
此处仍需留意有关刘萨诃的几个时间点,这与下文将要提及的刘萨诃西行一事是有重要关系的。刘萨诃出现时同样是三十一岁,但以375年至京师为限,当生于345年左右,比前文的推算要早二十一年,去向仍不知所终。
其后二百余年,唐初南山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又收录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故事,《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篇”《魏文成沙门释慧达传》载:
释慧达,姓刘,名窣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字,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母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闾,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520年)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逮(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建德初(572—578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575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581—600年)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初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
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道宣的其他著作中,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等,其记载基本相同。但是,事情在这里出现了变化:刘萨诃西行求法、至凉州番禾县东北望御谷时“授记”、不久就卒于酒泉、八十余年后瑞像从望御谷出世并昭示天下离乱等一系列离奇神异的事迹。
二、刘萨诃是否到过河西走廊
道宣对刘萨诃的籍贯、生卒年以及活动轨迹提出了新的看法,今人对刘萨诃生平的巨大争议也肇始于此。从道宣的记述中第一次看到了刘萨诃西行并卒于河西的情况,且刘萨诃预言“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引用道安碑的说法也是番禾“授记”最早出现的版本。道宣关于刘萨诃的记载,是在其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搜集资料、抄录碑文之后撰写的,文末他也提到上述内容“见于姚道安碑”。这个道安陈祚龙先生有考,就是北周冯翊胡城作《二教论》的姚道安。[5]道安作《二教论》,称佛教和儒教是“外教”和“内教”,道教则依附于儒教,实际上当时道安等人的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北周武帝“法难”的到来。
王琰和慧皎的著作中并没有述及刘萨诃西行求法并在凉州番禾县“授记”一事,但其事迹却出现在二百余年后道宣的著作中,道宣也是在考察中发现了姚道安碑才转引的。从“广有别传”、“备如前传”这样的文字来看,道宣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应当是看到过慧皎等人关于刘萨诃的记载的。发生在北凉的事情没有出现在早期王琰、慧皎的记述中,却见载于唐初道宣的著作,有意思的是道宣依然坚持己见,将刘萨诃西行求法及“授记”一事在不同的著作中多次转引。道宣游历过的这些地区,刘萨诃及其信仰是非常兴盛的,并且已经流传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从文中也可以反映出。道宣同王琰、慧皎一样,没有亲自到故事的发生地——番禾县去查看过,仅从道安碑的记载和当地百姓崇信刘萨诃的盛况就确定番禾县“授记”一事,理由尚不充分。
再看前文提到刘萨诃前后出现的时间。依道宣的记载,刘萨诃于435年到过番禾县并做了“授记”,但此事缺乏可信度。首先,年龄偏大。刘萨诃在各部典籍中第一次出现时的年龄都是一致的,皆为三十一岁。若按照王琰的记载,以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为限,至435年刘萨诃已年过古稀,况且文中之意其至迟在396年之前就已经到过京师了,以如此高的年龄西行求法,不免牵强;若按照《高僧传》云其“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到番禾县“授记”后一年(436年)殁于酒泉县城西七里涧为下限来算,已臻九十二岁高龄。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尚能翻山越岭,西行求法,实在难以想象,难怪陈祚龙先生也惊叹其“俗寿竟达九十有二”。而且慧皎的记述可信度要大于《冥祥记》,所以从年龄来看其西行河西一事尚不能使人信服。其次,出现和消失的突然性。《冥祥记》和《高僧传》二文记载一致,都不知道刘萨诃最后去往何处。但到了道宣那里出现了变化:“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也就是说最晚在太元末年(396年),时人尚能知道刘萨诃在京师或去往许昌,之后就不知所终了。在时隔近40年时间之久以后,刘萨诃突然出现在河西走廊的番禾县(今甘肃永昌县),而且没有他自东向西走过的广袤地域的记录,直接从江东跨越至河西,并且在这里做了这个从后世来看极为灵验的“授记”,他预言石崖当有瑞像出现,若是灵相俱备,则天下太平;若是身首异所,则天下大乱。此后“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又很快消失了。其时刘萨诃已是有道高僧,否则亦不会名列僧传。那么他在长达40年之久的时间里如蒸发了一般,这40年里他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史籍和内典均没有留下记载。从原来的江南、中原一带突然出现在河西走廊,地理跨度如此之大,并且在番禾县望御谷“授记”,挂锡云庄山,之后又“授记”莫高窟,之后再殁于酒泉。在河西出现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游历了这么多地方,办了这么多事,却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迁化于酒泉,着实令人费解。尚丽新先生认为刘萨诃西行求法之事本就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番禾县“授记”可能是出自河西走廊的一种传说,但没有具体说明传说的源头及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基于以上资料和论述,刘萨诃西行河西并在番禾县“授记”一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结论的成立,但它并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必然有其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三、隋炀帝改额感通寺与番禾瑞像及其信仰的流传
前文《续高僧传》载,“开皇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政权以后,大力弘扬佛教,不仅借此收买人望,还依靠佛教的一些理念来稳固其政权。且隋文帝杨坚因出生于尼寺,儿时为尼姑所养,甚至还为他取名,直至十三岁时方才还家。《隋书》(卷一)载:“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刘氏女也。及帝诞日,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割庄为寺,以儿委尼,不敢召问。帝年十三,方始还家。”①因隋文帝有在尼寺出生成长的经历,故其当政以后大力弘扬佛教是有缘由的,甚至达到了“佞佛”的程度。隋文帝的皇后等也十分崇信佛教,故开皇年间瑞像寺经像大弘是天下大势,各地的佛寺道场都很兴盛。因父亲杨坚佞佛,隋炀帝为东宫太子之时,崇信佛教也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君臣,西域各国向炀帝敬献广大土地、名马、表册等,以示顺服。而在此前,炀帝御驾亲征青海得胜后,过扁都口至河西走廊时遇到不测,其所属军马、随从等“死者十之六七”。学者多认为隋炀帝大队人马在通过高海拔且狭窄的扁都口时遇到了极端的天气,甚至考虑其是否因天气而引发了踩踏事件。虽时值夏季,但祁连山区高寒风大,亦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此处不再展开。隋炀帝是古代大一统国家中第一个亲征西域的国君,尽管其在后世的“声名”不好,称其为暴君,但不能否认其在一
定程度上开疆拓土的雄心和功绩。
隋炀帝在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君臣后,听说了瑞像寺有这样一尊十分灵验的瑞像,甚至可以表征国家命运的兴衰,遂亲至瑞像寺。“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从“躬往”等形容词看,炀帝对番禾瑞像的尊敬和信奉程度可见一斑。既然皇帝亲自诣寺礼拜,那么“厚施”和“重增荣丽”就是必然的事情了。隋炀帝杨广甚至亲笔将原来的“瑞像寺”旧额改为“感通寺”,“感通”当即有感而通灵之意,为佛教中表征灵验常用。“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炀帝在将“瑞像寺”改名为“感通寺”之后,又令随从摹写番禾瑞像的图像造型,让各地寺院依图供养。在帝王的崇信和推动下,瑞像寺改名为感通寺,番禾瑞像的造型为各地的寺院供养,那么瑞像本身所包含的和表征的信仰也就随之而流传开来。
现存各地的番禾瑞像,不论是造像、绢画、刺绣、壁画等,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内出土和现存的造像、壁画等,大部分的时代都在隋代以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隋炀帝的推动。炀帝下令各地依图供养番禾瑞像之后,借助皇帝的权力和崇信,番禾瑞像的形象及其信仰才广泛地传播开来,甚至在入唐以后,有更加兴盛的趋势。
四、现存与刘萨诃、番禾瑞像及圣容寺相关的文物
前文已提到,关于刘萨诃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是较多的,现存于各地的相关文物资料也很丰富。
今城关镇金川西村望御谷最西边的北部山崖下,仍能看到依山浮雕的瑞像像身。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的佛首(图一),原为县文化馆馆长在该村发现,后运送至县文化馆。佛首高约67厘米,为青石所雕,与像身石质迥然不同。头顶螺髻低平,肉髻已残损,面阔方颐,高鼻厚唇。造型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①依佛首比例量度,瑞像当与传说的“一丈八尺”相差不远。
20世纪80年代,于金川西村农舍发现一尊番禾瑞像造像(图二),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②造像为砂岩质,残高11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虽残,仍能看出其轮廓造型。头光后面,左肘下至仰覆莲台之间的空白处施有红彩。此尊也是番禾瑞像的造型,其时代尚存有争议。
炳灵寺石窟下寺窟区下层南段第13龛,龛为一尖拱形龛,高139厘米,宽74厘米,进深22厘米。龛内雕一立佛像,高97厘米。龛内造像亦为番禾瑞像(图三),其时代为晚唐。
20世纪90年代,于县城西南红山窑乡青龙山庙发现有唐代青龙山石佛造像一尊,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①。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雕刻而成,体量较大,是为“等身佛”。背后有舟形身光,顶部已残,沿上边弧顶雕有五身小化佛。佛像高170厘米,宽85厘米,体态丰膄,与真人几近相等。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捏衣角。衣服周边有锯齿状纹饰,背屏周边浮雕有嵯峨的山形。此尊正是盛唐时期番禾瑞像的造型。
另在圣容寺东临河处有一小型石窟,窟中残存有一尊北魏时期造像(图五),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造像为砂岩质地,残高114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去,舟形背光,上布有七身小佛,左手握衣角。②也是番禾瑞像典型的造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的第6窟为一平顶长方形的大窟,窟高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高浮雕一立佛像(图六),左右壁各雕一弟子像,为迦叶和阿难。主尊佛像高4米,水波纹高肉髻。沙武田先生认为该窟主尊立佛及胁侍二弟子像处山形中,当为凉州瑞像。但现在主尊造像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重修,已失去原有的面貌,幸得《河西石窟》记录了原来的佛像而得以辨识。
其他番禾瑞像造像还有山西省博物馆馆藏,出自山西万荣县唐开元年间的“李元封等造像”(图七),四川安岳石窟番禾瑞像③,日本高野山亲王院藏的金铜瑞像(图八)等等。此外绢画、刺绣和文献文本等主要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现在分藏于世界各地,英国大英博物馆、印度NewDelhi博物馆、法国及日本等地,此处不再赘述。
圣容寺前后山顶各有大小佛塔一座。寺后山顶大塔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图九),七级浮屠。第一层塔身较高,每边长5.44米,逐层往上收分,通高约12米。每级南面辟窗,当为通风、采光之用。塔内原有木梯通至塔肩部,后损毁。其内壁有唐“乾元元年”(758年)的墨书题记,另有“……一千五百人”、“圣容寺”、“番僧……”字样。整个塔造型简洁,外部轮廓呈轻微的抛物线,是典型的唐早期密檐式塔,与西安小雁塔形似,唯小雁塔南北两面皆辟窗,而此塔只南面辟窗。
寺前山顶小塔,亦是空心方形七级浮屠。第一层塔身较高,南面辟窗洞,东西2.13米,南北长2.26米,通高4.9米。此塔低矮,外部轮廓无抛物线,与西安香积寺善导塔外形极为相似。
五、与番禾瑞像有关的一些思考番
禾瑞像有多种称谓(“番”读“盘”),学界多称为“凉州瑞像”,莫高窟237窟榜题名为“圣容瑞像”,亦有因今之寺名称“永昌圣容寺瑞像”者,还有“凉州番禾县瑞像”、“番禾瑞像”、“刘萨诃瑞像”等,不一而足,但皆指今甘肃永昌县城北圣容寺后依山而立的浮雕瑞像,本文从“番禾瑞像”之说。
番禾瑞像有其固定的造型样式:立姿,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屈臂握住衣角,衣角长出手心,垂下的衣褶大致呈菱形,衣服边纹部分有锯齿状图形,身后背光有嵯峨的山岩,赤足立于莲台上。其中判断番禾瑞像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佛像身后是否能看到嵯峨的山岩或者类似于石崖、山峦等形状的背光。因文献记载,此像是“雷震山裂”而挺出的石像,佛像本身的背光与山岩的背景便很好地结合起来,也为番禾瑞像的造型提供了“理论支持”。
番禾瑞像的产生并非像文献中记载那般简单,也不仅仅是因为佛徒为宣扬佛教附会而“出世”,其必然是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结果。首先,地理位置的因素。番禾县扼守凉州西部,是丝绸之路和佛教东传的必经要道,有佛教传入的外部条件。“五凉”时期各路王侯争夺的目标都是“畜牧甲天下”的凉州,番禾县正是拿下凉州的桥头堡,实乃兵家必争之地,长年争战使得各个阶层都希望能安定下来,宗教就变成了人们“精神的鸦片”,佛教正好顺应了这个愿望。其次,与北凉的关系。北凉一朝,特别是沮渠氏迁都凉州以后出现了短暂的安定繁荣,人们当然不愿意回到过去。刘萨诃“授记”的北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即北凉沮渠牧犍永和三年,牧犍继位后其佛教活动比蒙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凉自沮渠蒙逊开始,就在都城凉州组织译场进行译经活动,这种大规模的译经弘法活动使得凉州也成为当时中国翻译佛经的中心之一,佛教已成为统治阶级和民间信仰的主流,大乘佛教的诸多重要经典在这里也被翻译出来,为此后大乘佛教的流行奠定了基础。435年刘萨诃在番禾县的“授记”也并非偶然发生,而明显是有意的安排,张善庆、沙武田二位先生在《凉州瑞像及其信仰的末法观》一文中也提出“末法”思想对具体年代的影响。再次,刘萨诃本人正是佛教徒宣扬佛法所需要的“榜样”。刘萨诃出家之前本是一个嗜好打猎的下级军吏,依理来看这样杀生犯戒之人业力深重,但是又似乎够不上“一阐提”,可他在“忽如暂死”以后放下屠刀,“顿悟”出家了,尽管大乘佛教的流行使得“人人皆可成佛”,但早期大乘思想的流行和不断深入人心正是由这样一个渐趋成熟的过程体现出来。再次,从统治阶层的角度看。尚丽新、杨君二位先生分别在《刘萨诃信仰解读一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和《民众佛教信仰的民间信仰化一以刘萨诃信仰为例》一文中对刘萨诃在民间信仰中的情况都做了深入和有意义的探讨。从另一个角度看,其“授记”能够预言“天下太平”、“国之兴替”这样的国家大事,这同一般的佛陀具有的能护佑功德主平安健康、治病送子及转世轮回的功能有所区别,其政治色彩比较强烈,而不是局限于民间。还有,刘萨诃在地狱冥游时受观音点化的经历,和魏晋之际地狱观念与观音信仰的流行有必然的联系。刘萨诃并非汉人,经观音点化,而后出家,而后成为高僧,而后成为利宾菩萨,而后成为刘师佛,这样一条逐级而上的完整的成佛路线,为修行者指明了方向,也赢得了他们的崇信。观音在这里又扮演了刘萨诃导师的角色,供奉刘萨诃实际上也就供奉了观音,这样好的事情之于佛徒和信众何乐而不为呢?出土自古浪县的圣历元年(698年)番禾瑞像,其碑身刻满了《心经》的经文(图十、图十一),
①《心经》是观音信仰的重要经典,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最后,番禾瑞像的称名。学术界至今都将其笼统地称为瑞像,而没有将真正的神格表达清楚,不论是早期提出后又被否定的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像,还是牛头山释迦瑞像、番禾瑞像等,都没有肯定其就是释迦牟尼或是其他的佛陀。众所周知,佛的诞生既需理论经典的支撑,又要通过造像来“藉像表真”,二者缺其一,就成了一条腿走路。番禾瑞像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一部成熟的经典来对它进行诠释,类似《道宣律师感通录》、《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稍有涉及,但都不足以说明。
六、小结
刘萨诃及其番禾瑞像的问题包含多个方面,这些问题都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笔者对刘萨诃西行河西一事的态度至今仍不能确信,因为其现有的资料不足以完全支持刘萨诃到过河西走廊,并做了这个也可能是河西佛教史上最为灵验的预言,遑论其“授记” 莫高窟、西游五天竺。刘萨诃的事迹自魏晋开始,历经隋唐五代宋各朝,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人们对刘萨诃的信奉反而有增无减,且不断加进了各种因素,因其预言而产生的番禾瑞像更是广受尊崇,其身上凝结了历史、民族、宗教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本身就非常值得探讨。实际上,目前大多数的讨论也集中在刘萨诃其人的“本生故事”和佛像发展史的讨论,还未能更加深入探讨其蕴含的哲理和要义。
刘萨诃是否到过番禾县“授记”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番禾瑞像在这里诞生了,不仅为当地僧俗所崇信,而且传播到了河西走廊以外的广大地区。有关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的问题仍需要不断探索,甚至可以汇集成一本专著。近来永昌县、炳灵寺、四川等地新发现了不少相关的造像、题记、雕塑等文物资料,可见其仍有新的研究材料出现,也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而继续深入地研究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相关问题,尤其对于中古时期历史、佛教、民族的交融发展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探讨的价值。
[美] 德效骞著 刘继华译
在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和县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用非常古老的中国对罗马称呼来命名的城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他们的城市起外国的名字。在那个清单上,有1500多个城市,只有其他两个城市使用外国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居住着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得出罗马帝国的人一定移民到了中国,并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似乎又不可能。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有着非常有名的丝绸之路,隔着4000英里的荒凉带,有沙漠和高山。横跨这条丝绸之路的是伟大的帕提亚帝国。这个国家对罗马的敌人充满仇恨,罗马从未征服过它。帕提亚人有效地阻塞了丝绸之路,从未允许任何罗马人自由地穿过他们的帝国。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通常允许贸易者的商队经过,但是他们阻止任何陌生人大量迁移。这座用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狭长的西北部。在公元前79年不存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是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的时候。也有名字由篡权者王莽命名,他用儒家思想来纠正名字,也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给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座城市他重新命名为揭虏(Jie-lu),这个词语包含两层意思:“在占领一个地方时拿下的胆小鬼【被俘虏】以及‘抚养的胆小鬼’”。然后,是不是中国人抓到一些罗马军团的囚犯,然后将其安置在中国西部边界以保卫边疆?古代中国将这座城市命名为骊靬(Li-jien)。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用来表示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后来用大秦(DA-TSIN)称呼罗马,中国政府同等对待这两个名字。骊靬这个名字是汉字对希腊名字“ALEXANDRIA”的抄写和缩写,本来表示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中国人不能区分罗马与亚历山大里亚。
在公元前110至前100年间,帕提亚国王的一个使团来到中国首都。在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当中,据说有来自骊靬的眩人。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眩人、舞者,无论男女都闻名于罗马世界。我们知道他们被送到国外。当这些人被中国人问到来自何处时,他们肯定地回答道“来自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单词自然地被中国人缩写为骊靬并用以表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关于罗马帝国和中国区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将欧亚大陆两端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60年,在罗马,罗马元老院将凯旋授予庞培(Pompey)将军。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到罗马,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助。恺撒(Caesar)和克拉苏(Crassus)来帮助他,并形成了第一次三人执政。恺撒在公元前59年成为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在公元前55年也成为执政官。后者后来成了叙利亚总督。克拉苏对三人执政贡献了大笔资金,这是其他两个人所缺乏的,但是他们的计划所急需的。同时他最缺乏和最想得到的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军事荣耀。他来到叙利亚之后,不顾他最好的将军的建议,向帕提亚人发动战争。公元前54年,他带着42000人进军帕提亚人的领土。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并不断发射一连串致命的箭。骑在马背上的帕提亚人在罗马人上来之前撤退,越过他们的马匹尾部发射,罗马人陷入无助境地。罗马军团只能形成一个方阵,在四周用锁盾来保护,这样就形成典型的罗马阵形——龟甲阵。但是帕提亚人朝罗马人盾牌的上、下方,毫无危险地屠杀了罗马人。到傍晚,20,000人被杀死,10,000人沦为囚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乘夜逃跑,到达叙利亚。我们不知道那些囚犯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迁至马尔吉安那(Margiana),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这是中亚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的梅尔夫(Merv)。这10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到马尔吉安那的安提阿(Antioch)的距离超过1500英里,俘虏在这样的行军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好的待遇。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古代诗人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迎娶了蛮夷妇女并服役于帕提亚军队。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中国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一个世纪,现在的蒙古被匈奴人占领,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人。他们的皇帝名叫单于。公元前60年,当他们的单于去世的时候,一场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导致8位请求者将自己立为单于。不久所有的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两个:单于呼韩邪(HUHANSIE)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郅支 (JZH-JZH)。当郅支在战争中打败了呼韩邪,后者从中国人中寻求援助,并派他的儿子给中国帝王做随从。中国的惯例是将结盟的外国王子控制在中国朝廷,一方面是作为他父亲良好行为的人质,另一方面是向他灌输中国文化和权力。郅支也派他的儿子来到中国朝廷。呼韩邪很礼貌地请求许可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朝拜,并表示其忠诚。他受到隆重的接待。宣帝很明智地把单于作为客人,并封他为与帝王一样的级别,位于中国人的王和其他高官之上。单于被给予丰厚的礼物,两个月后被护送回蒙古,在那里他被许可占领某些中国边远要塞。中国人支付高昂的费用以防止被匈奴人入侵中国边界。在这几年中,中国人因为呼韩邪的追随,送给他20000蒲式耳的谷物,这样他就能吸引大量的匈奴来跟从自己。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离开了蒙古,向西走去,试图与乌孙(WUSUN)联合,乌孙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或者吉尔吉斯人(Kirghiz)。然而他们杀死了郅支的大使,并将这个人的人头送到中国。郅支惊人地成功打败了乌孙的军队。但他不能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向北方前进并占领了现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国。1000英里的草原对匈奴来说不是很远,但比任何蒙古人以及其他草原骑士都远。
郅支认为在这里他会安全的。他于是向中国朝廷送了一封信,要求归还他那作为人质的儿子。守卫中国宫殿的校尉,谷吉(GUJI)(中国人的姓在前面,如匈牙利一样)负责护送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到达郅支王庭时,匈奴将谷吉和他的随从杀害了。同时康居(Sogdiana),中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郅支作为一个战士的名声很高,康居国王邀请他住在他的国家东部边界,在那郅支有着比寒冷的北方更肥沃的领土,能够保护康居免受乌孙的攻击。郅支害怕呼韩邪和中国人,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建议,签订了一个条约。康居送了数千骆驼、驴和马。然而在路上,旅行队遭受一场冻灾,只有约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康居。
国王对郅支表示欢迎并尊敬地招待,与他结盟,将他的女人送给他做妻子。郅支也将他的女儿送给康居国王。郅支现在深入乌孙国内,杀害乌孙人和让乌孙人成为奴隶,赶走他们的牛羊。乌孙不得不撤退,让他们西部的300英里国土无人居住。于是郅支变得骄傲,破坏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康居人。他为自己在都赖水(Du-lairiver)边建造一座有防御工事的都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塔拉斯河(RiverTalass),它的一条支流消失在锡尔河(Jaxartes)与巴尔喀什湖(LakeBalkash)之间的沙漠中。但是丝绸之路经过塔拉斯河,中国知道这座新城。中国本部西部有一位冠以西域都护头衔的官员,他有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自动化中国军队。当都护受中国皇帝命令出征时,在那个区域的小王国派遣军队予以帮助。
在公元前38年,西域来了两个年轻人,甘延寿做都护,陈汤为他的副手。甘延寿来自好的家庭,从未有过失。陈汤有进取心,勇敢,有计谋,但是不细心。
陈汤看到郅支单于在中亚发展一个大国的危险。他知道在本地辅助力量的帮助下,都护掌握的中国军队能够打败郅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获得安全保障,那将会太迟了。他的上级甘延寿赞同,但必须首先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远征的命令。然而陈汤指出这样一个请求会带来官方的耽搁,过于节俭的帝国朝廷将认为这样的远征太过昂贵。这时甘延寿病倒。
这对陈汤的诱惑很大。他大胆地伪造一个帝国的命令,要求臣属的政权派遣辅助力量,命令屯田的中国军队前来都护所在地开始远征。当甘延寿的健康好转,他了解到部下的行为,他感到吃惊,要求停止行动。但是事实上危险的行为即假造帝国命令的主要罪行已经犯了,不能够停止。因此在威胁和争论之下,陈汤说服他的上级来接受不灭的荣耀的机会。当一支40000人的力量集结,甘延寿和陈汤派人向东到朝廷送一个文件,谴责自己伪造帝国命令、集结帝国军队的罪过。在同一天,公元前36年的秋天,他们向西出发,前往撤回命令无法抵达的地方。
一半军队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路。另外一半在甘延寿和陈汤的带领下,走塔克拉玛干的北路,穿过乌孙国土来到伊塞克湖(LakeIssik-kol),然后向西。当他们进入康居时,陈汤与一些痛恨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达成秘密协议,这样获得有关郅支处境的关键信息。
汉语关于夺城的描述反映八个场景。这个描述一定来自绘画,和古代中国的图画一样,反映战利品、标明人和行动。不翻译原来的段落,这里我给出中国历史学家班固所写内容的大概。第一个场景:中国人的营地在距离单于都城1英里之处。城墙上挂着彩旗,士兵在喊:“过来打啊! ”城外骑兵飞驰,一百多名步兵采用鱼鳞阵排列在一个城门的两侧。
第二个场景:匈奴骑兵冲向中国营地,在营地的中国人竖起和装填好弩等待他们,在弩前,匈奴骑兵撤退。
第三个场景:中国军队在战鼓的推动下前进,团团包围城池,由大盾牌保护,射击城外的骑兵和步兵,他们正撤向城墙后面。一些人向城内塔上的守卫者射击,守卫者走下来寻求保护。但是从城外栅栏守卫者射杀许多进攻者,因此中国人火烧栅栏。
第四个场景:单于穿上他的盔甲,带着他的配偶和几十个女士爬上塔。所有人向中国人射击。但是进攻者击中单于的鼻子。许多女人被杀。单于也从塔上下来,登上一匹马,召集人到宫殿中战斗。
第五个场景:半夜过后。栅栏烧毁,余下的守卫者正逃人城中。一些人登上城墙,大声喊叫。城外和中国人四周有大批康居骑兵。一些人冲向中国人,被击退。
第六个场景:黎明时分。营地四周火在喷出。中国官员和人们在野蛮地呼喊,他们的钟声和鼓声震动大地。康居骑兵害怕,正在撤退。
第七个场景:中国人和联盟军在四周巨大盾牌的掩护下往城市推进。一些人已经进城。单于带着一百多男女,正跑进他的木质宫殿。
第八个也是最后的场景:中国人向宫殿放火,正努力争着进入。一些人进入,展开白刃战,已经致命地刺中单于。他的头被一名中国指挥砍下来。
现在我们仔细地注意这个记录的一些细节。首先,在第一个场景中有叙述一百多名步兵,采用鱼鳞阵排列在一个城门的两侧。“鱼鳞阵”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如此好的鱼鳞阵势的排列需要高度水平的训练和纪律。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或任何未开化的民族一定完成不了。牧民和野蛮人,像高卢人(Gaul)一样混乱地冲入战场。一个好阵形的排列只能由长期训练的人,比如专业士兵来完成。
这些人是希腊人吗?希腊人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离开大夏(Bactria)。而且马其顿方阵用小圆盾,大约直径一尺半。人们拿着它们难以足够紧密地挤在一起,出现鱼鳞的样子。
但是在那时罗马军团在步行的距离之内。他们靠战争为生。他们被一位著名的武士吸引,这位武士答应与痛恨的帕提亚人为敌。从阿姆河(Oxus)边帕提亚的边界到塔纳斯河边的郅支都城的距离为400~500英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以经典的罗马阵势——龟甲阵排列的人相距18年,这种阵法其他军队无法应用。长方形罗马盾的顶部的前面是圆形的,当一排士兵举着它们,靠在一起,一个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人以典型的中国人的视角从上面看确实像鱼鳞,除了罗马长形盾外,没有武器;除了罗马龟甲阵外,没有阵法能对中国历史学家的描述做出解释。
罗马人在郅支城的存在因重木城得到证实,中国人在城墙外发现重木城。希腊人不在城墙外使用重木城,但罗马人经常使用它们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前。那里的水上有一座桥。因此郅支明显在建筑防御工事时在工程学上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在他们给皇帝的报告中,甘延寿和陈汤陈述杀死1500人,相比郅支的配偶、后嗣、贵族和其他人,活捉145名俘虏,接受一千多人的投降,他们被作为奴隶分给为中国军队提供辅助的15个政权。当我们将活着的145人的数字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一百多的人数相比,我们几乎不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些145名罗马军团没有投降,但只是在他们的雇主被杀后停止战斗。他们可能保持阵形,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人群。他们实际上自由地选择跟随中国人。在中国罗马人相应地安置在一座专门建造的前线城市,对此中国人当然以他们对罗马的称呼——骊靬(Lijien)命名。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县城名单中,从王莽的命名中暗示居住在此的人是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获得,被抚养,这一切足以证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
罗马人影响的进一步证据是在事件中发现这次远征提交给朝廷的报告包括攻打的图画。这次胜利的记录能在我们读到的中国历史的编年史部分找到下面陈述:公元前35年2月,“因为单于郅支已经被处死……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现在关于“图书”展示给皇帝的女人的叙述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是何种物品,对于女士来说感兴趣?地图、君主的记录和类似文件肯定不会是后宫女性所寻找的事物! 这些女士几乎不能读书,这种文件太珍贵而不能由女人玩弄。一定是这次胜利的图画——班固以描绘场景的方式叙述战役确定了这个结论。
今天充足的证据表明前汉时期的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绘画艺术。中国将军穿越之前未知的道路的事实将有他们道路的地图。一幅去康居的路线图需要长布卷(尚未发明纸),附有沿途的风景的图画。关于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其他图画。
前汉时代的中国画,我们已经有许多描述,只是涉及名人、道德故事和传说。除了陈汤的报告我们知道没有当代事件的陈述。这些攻打郅支城的画在中国绘画中是前所未有的。它们说明中国艺术的一种新变化。
然而在罗马人的胜利中使用画是众所周知的。当陈汤与罗马军首领交谈时,这个人讲述了罗马人胜利的庆典。其中一些罗马人可能参加公元前60年庞培的胜利。关于维斯帕先(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的胜利,约瑟夫(Josephus)说:“战争有许多的陈述,在单独的部分,用一张关于有趣事件的、非常逼真的图画来展现。” 罗马人实践的描述非常符合陈汤放在路线地图上的图画的性质。而且这种关于生动地描述一场战争的记录在整个班固史书中是唯一的。
因此在公元前36年,陈汤在中亚遇见一百多名克拉苏罗马军团,将他们带回中国。远征的汉文记录以一个词语描述他们的军事组成,这在中国文学中别无其他,这只与罗马军队使用的龟甲阵相符。被中国人包围的匈奴城由重木城防卫,这不被中国人和希腊人所应用,但经常被罗马人应用。通过图画再现军事战争场景的实践被罗马人用于他们的胜利,但在中国前所未闻,这成为中国人远征报告的一部分。比其他任何事件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公元前79年和公元5年之间,发现中国有座城市有中国人对罗马的称呼——骊靬,这个名字表明该城居住着来自罗马帝国的人们。
中国的罗马城存在到公元746年,当时藏族人占领中国的那部分。1世纪之前,一个伟大的中国学者在中国的首都、位于中国西部的长安,他的著作说起那座城的人们对这个地名的特殊发音。他说那些人将这两个词的中文名混在一起,将它拼起来像“liakh-ghian”。他们可能在拼“Alexandria”中的“x”,“x”用中文拼不出来。因此罗马也为多种族居住的现代中国做出贡献。
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译自HomerH.Dubs, ARoman Cityin Ancient China ,GreeceandRome, Vol.4,No.2(1957),pp.139-148.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节选)
张维华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其音义不类汉名,诸家注释,言各有殊,未能归于一是。前曾著文,稍加讨论,今复检阅,尚觉未安,故复论之。按骊靬县之名除见《地理志》外,又见许氏《说文》革部靬字下,云:“靬乾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改骊为丽,以靬训革。清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因其说,以为丽靬县之得名盖取义于丽皮,且以骊为误字,云:“《说文》,靬,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是许多氏所见《汉志》作丽字,盖取丽皮之意,以氏其县。若作骊靬,是以深黑色之乾革为县名也,于义无取。”揣《校注》之意,盖以骊靬县华丽之皮也,骊靬为黑色之皮也,而骊靬县当取义于华丽之皮。按骊训为深黑之色,亦见《说文》马部骊字,云:“骊,马深黑色;《校注》所言,即本乎此。”其字虽与丽有别,但因同声可以互用。《史记·周本纪》载申侯弑幽王于骊山下,《水经注》引其事作丽山,云:“遂败幽王于戏水之上,身死于丽山之北。”《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死,葬于骊山,《渭水注》引其事亦作丽山,云:“鱼池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左传》庄二十八年传载:“晋代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渭水注》引其事,于骊戎骊姬之骊均作丽,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冯迳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且《史记》之文,亦不尽同,一编之内,骊丽错举。始皇三十五年《本纪》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工,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此丽山即秦始皇葬处之骊山也。许氏于骊靬县之作丽靬,有类乎此,非有深意,《校注》必强分之,因而断言骊靬县之正文当为丽靬,且其得名之由来,乃取于丽皮之意,似有未合。至于许氏以骊靬县属于武威,而不属于张掖,《校注》未言及之。惠栋《读说文记》云:“丽靬,两汉皆属张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地理志》张掖郡骊靬,《郡国志》骊靬亦属张掖,许系之武威,未详。”王鸣盛《蛾术篇》云:“武威有丽靬县,骊靬前后《汉志》皆属张掖,疑许慎时曾改属,史失载。”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云:“《地理志》《郡国志》骊靬县属张掖,《晋志》属武威。此云武威者,《武纪》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许氏或据未分时图籍。”罗振玉《说文解字校录》引顾氏说:“丽靬,《地理》《郡国》二志属张掖郡,《晋志》乃属武威郡,或《后汉》此县即改隶,否则非许氏原文矣。近人辄谓此据汉武以前言之,恐无此理。”按东汉无骊靬改属武威之事。《后汉书·郡国志》载武威郡所属诸县,其自张掖郡划归者,仅有显美,未有其他。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征引颇详,亦未言及骊靬之并于武威。《汉书·张骞传》《注》引服虔语,亦言骊靬为张掖郡。虔为东汉末年人,上与许氏相接,相距不远,其间似不至有何变化。此盖因张掖、武威两郡毗连,县邑交错,易致混乱,许氏不慎,偶尔误引,必非别有他故。《蛾术篇》疑许慎时曾改属,是乃过信前人之说。《说文校议》又疑许慎所据为元鼎六年之图籍,更属虚臆曲解。许氏而后,曾注意及骊靬县者,即为服虔。《张骞传》有:“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靬、条支、身毒国”之语,《注》引服虔语曰:“犁靬,张掖县名也。”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犁靬之国发生关系。犁靬,张掖县名也。犁靬之国首见《史记·大宛列传》,作黎靬,《张骞传》改作犁靬;《西域传》又改作犁靬。《后汉书·西域传》又改作犁鞬,亦言亦名大秦。所举不同之名称,除大秦别有他说外,均属国音之异译,此乃历史上常有之事,不足为怪。服虔以西域国名当张掖之县,必有史实为其背景,惜未言明。师古重申服虔之说,但于所最关切之史实,亦未指出,云:“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声相近,清儒或有从此说者,其所发明亦鲜。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武威有骊靬县者,《两汉志》骊靬属张掖。”《汉书·张骞传》,抵安息,奄蔡、犁靬。服虔曰:“犁靬,张掖县名也”,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云;“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犁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按石州之说,足以破《地理志校注》说之惑,而于骊靬县得名之由来,亦较具体,然所以因其降人而置县者,亦阙而未详。熊得山译日人关卫《西方美术东渐史》第三章论《中国中原西方艺术之传播》,言骊靬得名由于犁靬国人之曾居于此地。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言张掖郡之有骊靬县,乃由处置归义降胡而设。1936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之《亚洲研究》第三四合期,内载卜德贝尔格一文,题为《中国边疆史札记二则》亦论及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其说与以上所言尽同。窃意骊靬置县,或与犁靬来华之人有关,而此辈来华之犁靬人,又当是《大宛传》所载安息进献之眩人。然必须证明安息所献眩人,果留华未返,且又确处河西,方能使此说信而有证。除以上所举二之外,论及此问题者,仍有数家。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以骊靬之得名,原于地理之形势,云:“今黑城驿在山丹县南。骊靬本属酒泉,与删丹人同时徙此。骊,俪也,靬音杆,射者所以杆臂,即拾也。故骊靬在今玉门县北百余里之华海子侧,有废城二,西有布鲁湖,接华海子,象两靬相俪也。”昔年,在成都,偶读蒙文通所著《周秦民族史》,内有《秦为戎族》及《秦即犬戎之一支》二文,言骊靬为山之异译,云:“《秦本纪》称申侯言:‘昔我先俪山之女,为戎胥靬妻,生仲,保西垂。’班固《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中国安得有天子曰骊山女,斯其为西戎种落之裔欤! ……骊山女在殷周间为天子,彼时西戎之强者,前则鬼方,后则犬戎,力足以侈天子之号,非此莫属。《秦本纪》言:‘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 《周本纪》言:‘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括地志》云:‘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十里。’《土地记》云:‘骊山即兰田山。’此骊山之名,与骊山女必有相联之关系。然殷周时西戎之天子,不容得在兰田,谅骊山原在西裔,此骊山之女号所由始。及其既入关辅,而新丰因有骊山之名,亦如陆浑之戎出瓜州,及既至伊川,而伊川之山以陆浑名,大荔在泾漆之北,及既至临晋,而临晋得大荔之名。《国语》云:‘幽灭于戏’,《左传》疏引《纪年》,亦云:‘幽死于戏’,则亦以犬戎之事,而后戏有骊山之名。是杀幽王之犬戎,即骊山女之族,亦即骊山女与秦皆犬戎这证也。骊山之后曰秦,亦犹《后汉书》言大秦国亦名犁鞬。犁鞬于 《张骞传》作犁靬,《匈奴传》作黎汗,《说文》作丽靬,皆一音之异译,骊山亦此之异译也。《汉志》张掖郡有骊靬,此当为骊山女为天子之所在,,于今为永昌县南,则固昔西戎地。古天子有骊连氏,或作骊畜氏,殆即作骊山女耶?”余前著《骊靬县得名之来原》一文,登载于《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以为祁连山为霍去病立功之所,甚为时人所注意,而其读音又与骊靬二字为叠韵,有通转之可能,因言骊靬之名,为祁连之别音,而骊靬县之得名,乃原于祁连。按此所录三说,吕调阳弊在过于推求字义,殊乏历史上之根据。蒙文通说,言之虽足成理,但亦有牵强附会之嫌。殷周间是否有骊山女为天子事,已属疑问,而骊山女为天子之地,又何以知其必在今甘肃永昌县南?汉开河西之地,建郡置县,又何以采用千数百年前空无着落民族之名,自不能不令人生疑。至于余之所论,亦有人认为不易成立。盖祁连之名,前书所载未有他称,汉人立县,何以不采用最习见之名称,而必用最生僻之骊靬二字,自亦难解。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
——本文选自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的《汉史论集》
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
王宗维
骊靬位置应在条枝西北。《大宛列传》安息、条枝均有专条,而不列骊靬。《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记西志犁靬条枝接,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而不载到犁靬的距离。安息条记武帝时安息“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证明骊靬与安息相邻,此时成为安息的属部。证之条枝国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诸语,可知骊靬是一种民族,以其善于幻术著名,先是臣属条枝(塞流息咨王朝),条枝衰亡后,其一部分又成为安息的属部。安息极盛时的疆域,西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则骊靬人大概就在此西北。西汉武帝时汉朝使臣所到的骊靬,就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
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罗马国家的势力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比提利亚、本都王国,并于公元前64年前后消灭了塞流息咨王朝的最后势力,将其并入罗马尼拉领土,从此罗马与安息就以两河流域为界,安息役属下的骊靬人大部成为罗马的属民,罗马设立行省统治之。自此以后,汉朝政府与骊靬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了与罗马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汉朝与罗马就开始了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即罗马,汉朝人先是同骊靬人发生关系,从罗马统治骊靬后,汉朝又是通过骊靬与罗马政府接触,所以就产生了大秦又名骊靬的说法。这种不确切的说法,大概和东汉永元九年(97年)甘英出使地中海地区返回的报告有关。
骊靬人来中国,至晚从武帝元鼎年间已经开始。《大宛列传》说:“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汉使第一次至安息,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所派的副使,返回时间在元鼎三四年,安息献犁靬眩人,亦应在此时。由于汉武帝喜欢犁靬眩人的幻术表演,并令汉人仿效,此风更甚。《大宛列传》记:“及加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正义》释:“加其眩者之工,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犁靬。”说明梨靬眩人不但把幻术传入中国,而且汉朝迅速将这种幻术发展、提高,成为风行一时的技艺。这种眩人幻术,根据注释家的解释,相当于当今魔术。《史记索隐》引韦昭注:“眩人,变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息解。”《汉书·张骞传》应劭注:“眩,相诈惑也。”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通典》还记武帝时安息国所献犁靬幻人的体貌特征是“蹙眉、峭鼻、乱发、拳须”。这种特征,同《大宛列传》所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有所不同。由于骊靬幻人到中国受到汉朝政府的重视,所以后来陆续来中国者不少。西汉时张掖郡下辖骊靬县,《汉书·张骞传》骊靬条下颜师古注:“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又五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声,无定字。”骊靬的读音,颜师古注:“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由此可以说明,骊靬县的得名,与犁靬人有关。他们随西域各国使臣来汉,有的在河西待诏,不能返里,寄居在河西。因为他们善于幻术,所以远道来此寄居的西域各国人都被称为骊靬人,晋时称骊靬戎。汉朝政府为了进行管理,于其地设骊靬县。骊靬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更多地见于居延汉简中,大概在武帝后昭帝时,即有此县。骊靬人定居于河西,有的到达长安,虽然人数不多,但它说明西汉时汉朝已经和罗马东部辖境的骊靬人有着交往,骊靬幻术在汉朝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王萌鲜说骊靬
王萌鲜
一、两个伟大皇帝的憧憬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无独有偶,还有一句,叫相辅相成。小事物是这样,大事物也是这样。公元前1世纪,世界的西方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同一个时间,世界的东方也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西汉王朝。罗马帝国发展到恺撒、庞培、克拉苏“三巨头同盟”时代,已变得空前强大;同时,东方的西汉王朝发展到汉武帝中期,也变得空前强大。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亚、西亚传到了欧洲,也传到了罗马帝国。据罗马史学家卡希攸斯的著作记载,在一次向凯旋的将士授奖时,当恺撒大帝把中国生产的丝绸授给有功的将军的那一刻,几乎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这到底是什么呀?柔软而轻盈,坚韧而新颖,光滑而精致,颜色鲜,光泽斑斓。这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丝绸织品。恺撒说:这些东西来自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国家叫“赛里斯”,即“丝国”的意思。“赛里斯”这个名称也是几经翻译才传到罗马帝国的。老实说,中国的丝绸织品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高科技,犹如20世纪美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罗马皇帝十分神往东方遥远的大帝国,萦绕于心,情难自已,特别想跟这个神秘的东方之“丝国”取得联系。然而,有一个国家首先阻挡他们,这个国家,中国汉代称它为安息,即波斯国,今天的伊朗一带。安息把中国获得的丝绸等高新产品转手卖给古罗马,从中取得高额利润。这使罗马人十分愤怒,于是他们不惜发动战争打通走向中国的道路。古罗马皇帝对中国的相思之情何等深切!
遥远的东方大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传奇式地发展着。安息对罗马冷,对中国却特别热。汉武帝的特别使团到安息国界,安息王派官员及两万骑兵奔波数千里,到东界迎接中国使团,浩浩荡荡,经过数十城才迎接到首都,空前隆重。中国使团返回时,安息派使团一同前来,到中国后,向汉武帝献上大鸟卵和高级魔术师。汉武帝在金碧辉煌的甘泉宫里接见了安息国特使及高级魔术师。一听介绍,才知道高级魔术师的家乡,正是以前张骞提到过的骊靬,即古罗马。魔术师当场向汉武帝表演了口喷火、嘴吞剑的技艺,在这一刻,也使汉武帝和在场的所有中国官员为之目瞪口呆,震惊不已,随后都赞不绝口:神、神、神! 汉武帝向魔术师仔细询问了古罗马的国情及社会风貌。从此,这位中国皇帝对那个遥远的西方大国罗马,梦萦神牵,情有独钟。对待这位罗马魔术师也就特别宠爱和尊重,甚至每次外出巡行时,也一定要带上罗马眩人。这些历史场景,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以生动的笔调做了描述。
真是叫天天应,叫地地灵,中国皇帝和古罗马皇帝的历史情怀,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朵,最初的憧憬结出了友谊之果,谁能想到,汉武帝去世四十年之后,竟然有数千古罗马士兵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中国,中国西北角竟然出现了一个以古罗马国名骊靬二字命名的县份。这个骊靬县的遗址就是今日永昌县的者来寨。
也许有人要问,真的有这个县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
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对骊靬县,中国史书有明确记载。
二、骊靬县,史书记载明确
对骊靬县,史书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或有关地理的篇章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记载。譬如《汉书》说:张掖郡辖县十个,有番和、显美、骊靬、鸾鸟等。这四个县都是永昌古县。当时番和城在今天的焦家庄,显美是今天的清河。有的史书某些文字还表明,骊靬县在番和城附近,靠祁连山。清代康乾时期编成的地理巨著《大清一统志》又十分肯定地指出: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城南者来寨。元代有《大元一统志》,明代有《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大清一统志》是前两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确认骊靬废县在者来寨之见,早于清代。
骊靬县到底建立于西汉何年?没有明确记载。但经过后来特别是现在一些学者的考证认定,它的建立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之间,或者说在公元前45年前后。后面我还要细说。它的撤销时间,史书倒是给予了明确的表述。《隋书》说:开皇中,即592年,隋文帝下令将骊靬并入番和,骊靬以县的建置存在630多年。《晋书》说,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这些文字,不是十分清楚地说明:骊靬县南依南山,北靠番和吗?这样的地方当然就是者来寨了。
那好,既然有这个县,永昌旧县志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某些老祖宗,特别是当时修县志的那些文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县的存在。我们知道,《大清一统志》,乾隆十一年完成的《五凉志》,都明确写了这个县,我们的旧县志乾隆本在编写时参照了《五凉志》,但却删去了骊靬县,为什么?一则,按字义解释,骊靬就是黑色的干牛皮,多可厌! 二则,骊靬又是一个西域番邦之国名,多可怕! 前者和牛联系,我们汉语中有多少美丽动听的词儿,先人偏偏用骊靬二字,后者和番邦联系,他们当然接受不了,删去为好。上世纪40年代,永昌陈世增又写了一个续修本,是手抄本,他明确写进骊靬县,遗址即今者来寨。
骊靬县的存在既已明了,那么,它又是为何而建的呢?这就是我要马上接着说的问题:骊靬探索之旅。
三、骊靬探索之旅
骊靬因何而建?史书正文都没有明确回答。但西汉王朝用这么两个古怪的字来作县名,必有它的深意在里面,不可能是随便而呼的。班固老先生在《汉书》中没有说明,就把难题留给了后人。于是后来的学者就开启了骊靬探索之旅。骊靬探索,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我分别说来。
第一个阶段,是发轫阶段,代表人物为应劭、服虔、颜师古。《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巨著,由于内容翔实,结构严密,文字赡富,很快被世人推崇,但也比较深奥,有许多地方读者弄不明白,于是不少人为之注解。注解者东汉末期最有名最有成就的是应劭和服虔,两人都是博览群书善著文的经学家,所生年代比班固晚七八十年。《后汉书》有他们的传。他们对骊靬县做了解释。应劭在他的《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服虔在注释中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东汉称古罗马帝国为大秦。又过了五百年,唐太宗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颜师古,对《汉书》做了全方位的诠释,他说,他的诠释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后来,也确实被历代推崇为最好的注释本。他解释骊靬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这三位先哲的话,连起来就是:以大秦国国名取名的骊靬县,是为到中国来的一批西域异族而建的。颜师古还特别指出:骊靬,当地居民自呼曰力虔。师古又特别指出,虔字此处读“揭”,就是说,居民自呼曰力揭,自称曰虔(揭)人,这可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实际上已揭开了一个特殊族种的谜底。后面将要细说。
第二个阶段是考证阶段。时间到了清代,大家都知道,满族建立了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界最黑暗残酷的时代。殃及全国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使文人们不敢说话写文章,文人们只好转头去研究古董。这样,事情的另一端出现了好现象:一个空前的考古、考证时期到来了,训古之风大兴,因此清代的古籍考究成绩非凡,为前代所不及。对骊靬的探索也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明确地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宣布:汉代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换句话说,骊靬县为归顺的大秦国人而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惠栋、钱坫、徐松、张澍、王筠、张穆、王先谦等,他们从康熙到光绪几乎囊括整个清代,对骊靬的考证形成了一个研究链。这些人,都是博览群书,学术造诣深,研究态度严谨而名载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像惠栋,是承前启后的大学者;像张穆,后人评价他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学,尤精西北地理文学,对历代各民族交往关系,考证精确,见解独到,极受学界推崇;像徐松,学界认为他对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卓著。这些学者一致认定: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此结论可以说是金声玉振,一字千钧。他们把应劭说的“西域蛮族”身份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了。
第三个阶段是开拓阶段。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新纪元,也为骊靬探索注入活力,注入新的文化元素。骊靬探索中出现了一批崭新的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文化运动,熟谙古今,学贯中西,思维活跃,视野开阔,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于一身,敢于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视自己所占领域的是与非,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发现新的境地,得出更精确的学术结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向达和冯承钧两位先生。
向达,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年至1938年,又到牛津大学、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冯承钧先生幼年出国,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尤精于中西交通史研究。二人都是学术巨擘,史界泰斗。不仅心中铭刻着中华泰山的庄丽,也目睹了欧罗巴阿尔卑斯山的雄伟;不仅对唐尧虞舜汉武唐宗研究透彻,而且步入希腊罗马殿堂窥其阃奥。因此,他们可以用更新的视角、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骊靬的本源。
向达在自己所著的《中外交通小史》一书中说:“中国史所记述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但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骊靬、大秦、拂森,都是指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向达先生明说了,骊靬县即为归义罗马人而设。冯承钧在他写的《西力东渐记》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匈奴,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罗马人从何而来?冯承钧认为,他们来自入侵波斯的古罗马军团,是失败后的古罗马军团的游勇散兵。这是一个大突破,说明公元前36年,流亡于中亚一带的罗马士兵,他们确系来自卡莱战役失败后的克拉苏的部队。他们徘徊在中国的西大门口。
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谦先生发表了自己的惊世骇俗的长篇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他在研究古罗马战争史的时候十分关注入侵安息失败后罗马大批流亡士兵的下落,终于从《汉书·陈汤传》中发现了他们部分人的身影。他得出了和冯承钧先生同样的结论:一支罗马部队参与了北匈奴郅支单于跟汉军的作战。汉军统帅陈汤把他们俘获后带入关内,在张掖郡设立骊靬县作了安置。德效谦之说,我们可以概括为“陈汤俘获说”。这是骊靬探索的第三阶段,是开拓,是突破,也是中西文化大交融后骊靬探索必然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是张扬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正本清源阶段。骊靬探索在第三阶段后变得悄然无声。时间进入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个年头。和西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空前深入。1989年下半年,《参考消息》及《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的消息,说的是:经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和几位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研究,认为西汉的骊靬县是为安置一批古罗马战俘而设的。他们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府副都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击败北匈奴郅支单于,俘虏了一批罗马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河西走廊,设置县城以领之。这其实是重申了德效谦之说,但在当时经媒体炒作,引起了靬然大波,震动了史学界。本人接着发表出版拙作《骊靬书——支古罗马军团的最后归宿》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尔后,中央电视台介入,《东方时空》、《走近科学》等栏目都多次报道,骊靬的话题推向世界,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但这些宣传和报道,都讲的是“陈汤俘获说”,由于“陈汤俘获说”存在致命的缺陷,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如葛剑雄、刘光华等教授的反驳,反驳的根据也在《汉书·陈汤传》中。因为《陈汤传》讲得十分清楚。书中说此次战役,“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也就是说,陈汤将军把所有的俘虏分赋给了参与汉军作战的十五个在西域的诸侯国,未带一人进关。这种反驳当然也是致命的,将“骊靬县与陈汤有关”的说法彻底击碎,所以“陈汤俘获说”,只能说陈汤的俘虏中有罗马士兵,但与骊靬建县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骊靬探索之旅到此止步了吧?不! 没有止步。“陈汤俘获说”只是探索中的一个分支,探索还正在深入。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常征教授,在1992年第一期的《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以翔实的史料,以严谨的分析,以学者应有的眼光和勇气,探讨了数千罗马兵归顺中国的过程。常征的结论是:古罗马军队在安息失败后,突围的第一军团六千多人辗转到了安息东的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并基本定居下来。公元前40年,大月氏发生“五翕侯”互并的大内战,被排斥的罗马人,越葱岭,傍昆仑山北麓进入河西,归顺汉王朝,另曰“义从胡”,汉王朝为安置他们而设骊靬县。因为他们是由大月氏国归顺的,我们把这一说概括为“月氏归义说”。
另外,不能不特别指出《辞海》关于骊靬的诠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有数百名学者参加,从1958年开始,到1965年完成修订,于1979年再修订后出版的百科综合大辞典《辞海》,在“骊靬”条目下解释道:“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这就是说,骊靬县,为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而建。这一说法,我们称为“骊靬内迁说”。
通过我们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已经明白,对于骊靬何以设县的探索,经过了四个阶段,即起步发轫阶段、深入考证阶段、开拓突破阶段、讨论张扬阶段。时至今日,骊靬何以建县出现了三种说法,即“陈汤俘获说”、“月氏归义说”、“骊靬内迁说”。同时,通过以上回顾,我们还得以明白:首先,对骊靬建县的探索已经过两千年时空,连绵不断,逐步深入,逐步明确,不是某些人说的“子虚乌有”;其次,探索中留下重要论断的人,东汉有应劭,唐代有颜师古,清代有惠栋、顾祖禹、张穆、王先谦等,现代有向达、冯承钧等,他们或者是训诂大师,或者是经学巨儒,或者是史地泰斗,他们一言九鼎之见,光照史册,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空穴来风”;再次,探索者们也许方法不同,叙述有别,但在认知上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骊靬即大秦国,大秦国即古罗马,骊靬建县绝对跟一批骊靬人有关,即跟一批古罗马人有关。汉武帝时期的骊靬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争论。但东汉时期,则认定大秦国即古罗马。《后汉书》说“大秦国一名黎靬”,即骊靬。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三种说法,首肯的当然是“骊靬内迁说”。一则,《辞海》是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的重点项目,是国家科技方面完成的全局意义的系统工程;二则,《辞海》的修订,投入了来自全国各界各领域的学术精英近千人,潜心研究,反复论证,去伪存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三则是它的修订,竟然经过了二十年沧桑岁月的洗练。因此,它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更大的精确性,更广泛的认知性。“骊靬内迁说”,涵盖了清代学者的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建的论断。降人不是指俘虏,而是指归顺、归化、归义、亲附。常征先生的“月氏归义说”和“内迁说”是一致的,不过说得更具体,认为这批骊靬人是从大月氏国越葱岭、沿昆仑山进来的。
四、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
是呀,说法种种,骊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或者说:古罗马人到底是怎么进入阳关的?这里具体谈谈我的看法。讲四点:一、形势;二、时间;三、路线;四、具体办理人。
(一)形势:我们已经知道,古罗马帝国为打通走进东方的路线发动了对安息的入侵。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七个军团四万多人的部队进攻安息,结果在卡莱遭到安息骑兵的围歼,罗马兵有六千突围,一万被俘。这一万俘虏被送到安息东界守边。近两万罗马士兵稽留在中国西界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安息东界和大月氏接壤。被俘者被当作奴隶看待,不堪忍受虐待而大批逃亡,而沦为难民。突围的罗马兵则成为游荡在中亚盆地的游勇散兵。大月氏既是安息的友谊之邦,也是西汉王朝的友谊之邦。此时,穿过大月氏通向安息的丝绸之路,则显现出“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繁荣景象。汉天子广修文德,恩被天下,让四方来服。条条大路通向长安。西域都护府本身就有接纳归附者的重要任务。大批无家可归的古罗马士兵徘徊在中国西大门,进关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二)时间:指日可待,到底是何日?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德效谦,哈里斯等认定的公元前36年,另一个是常征先生认定的公元前40年,前者,我们前面已经说清,公元前36年陈汤俘获的罗马兵并没入关,已就地分散管之。后者,说的是已定居大月氏的罗马兵因大月氏内乱而逃亡中国,似亦理由不足。按照常理,已经定居,就有了起码的产业,起码的生活资料,不可能轻易离乡背井,弃家而逃。他们进入中国而又被设专县管理,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一是他们必须是流亡者,而不是定居者,只有流荡不定才会寻找栖息地;二是进关以后汉王朝为他们设专县,必须是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人数至少在两三千人以上,否则是不会设县的;三是他们在大月氏、康居等国流亡,时间不能长久,流亡时间过长,人员会自寻着落,队伍就会自行瓦解,也就没有了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卡莱战役是公元前53年,安息西界至东界相距约两千公里,突围的罗马兵团以及被俘的万余人转移至安息以东,需一两年时间;再经逃亡、流动和组合过程,又需一两年时间。这时,一支庞大的难民队伍已经形成。他们是一批职业军人,习惯于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他们与周围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出于生活的需要,必须组织起来;还由于当地居民或许对他们心存戒心甚至敌意,处处设防甚至要消灭他们,为渡过一道道难关,他们必须暂时结成一个群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体弱有病,或者有伤,不能奔波,只好留在当地听天由命了,而由强者结成的难民群体,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极力寻找着落脚安身的地方。因此,我们断定,数千古罗马兵进入中国,时间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最迟不超过公元前45年。汉骊靬县,就是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设的。
(三)路线:历史事件,总是会在史书中留下蛛丝马迹的。我们读《后汉书·西域传》,会在于阗国中发现一个十分新奇的地名:骊归城。《西域传》文字的叙述十分新奇地告诉我们:骊归城之名得于西汉。为何叫骊归城呢?顾名思义,骊归城就是欢迎骊靬人归顺的城市。可以想见,当年,西汉王朝的使者在这座城市举行了一个大会,欢迎数千骊靬人归顺中国,因为有重要的纪念意义,这座城市即改名为骊归城。丝绸之路南线经过于阗。流亡于西域的数千古罗马人就是从南道经于阗,进入阳关的。骊归城和后来出现在张掖郡的骊靬县形成惊人的呼应。骊归城成了古罗马兵进入中国的历史见证。
(四)具体办理人:班固的《汉书》为一个叫辛庆忌的人立了传。辛庆忌是狄道人,即现在的临洮人。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0年,他就是张掖郡的太守,以后又到酒泉郡当太守。书中说他到张掖前并不知名,但到张掖郡当太守后,一下闻名朝野,成为名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书中这样写道:前在边郡,功劳卓著,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为国之虎臣。“西域亲附”作何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和平年月,辛庆忌完成一桩使西域亲附的大事,再具体说,就是辛庆忌作为汉使,前往于阗迎来一批古罗马人到张掖郡,并为之建县。这样解释有何不可! 因此,我认为骊靬县的具体建置人就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
“先生,你的这种分析有点捕风捉影了吧?”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遗案,有两类:一类证据确凿,另一类证据不全。历史学家为历史事件做出论断,不是为史料充足的事件去做人云亦云的复述或说明,而是为史料欠缺的事件做出合情合理而被后来历史证明正确的判断。正如一个高明医生去解决罕见的疑难杂症一样。要不,我们要历史学家干什么! 捕风捉影,正说明有“风”可捕,有“影”可捉。顺影寻去,影子后面难道不是事物的实体吗?张掖郡出现了一个骊靬县,而汉王朝远在万里之外的属国又有座骊归城,无论如何,不能视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既然有骊靬人归顺,就得给他们一个落脚处;有数千人,就应当建县。
五、虔人、羯、秦胡、卢水胡,原来都是骊靬人之称我们再来察看,骊靬县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中国史书对照面山下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做出了具体而又精彩的描述。骊靬人的生活画卷光彩照人。
《晋书》载:永和十年(354年),凉王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这是史书对骊靬人的最直接的描述。那些反对“骊靬即古罗马,骊靬戎即古罗马人” 之说的先生们,从未直面这段文字,从未做出追根溯源的探讨。
我们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统史书对于古凉州地区特别是河西的少数民族叙述中,总是会碰到这些民族概念:秦胡、卢水胡、力羯、虔人羌、骊靬戎,等等。其实,它们都是骊靬人的称谓。骊靬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东汉时期,中国称古罗马为大秦国,这没有丝毫含糊。因此,骊靬人被称作秦胡,也有时叫卢水胡或虔人。三国时期,骊靬人主要被叫作卢水胡,有时也叫秦胡。两晋及南北朝时期,被称作羯、力羯、骊靬戎等。
这不是胡说,有史为证,让我们一一道来。
先说羯。史书中东汉以前没有羯,东汉开始有了羯,或称羯胡,或称羯人,或称羯族。羯从何来?来自骊靬县。这是唐朝大学者颜师古告诉我们的。师古解释“骊靬”二字的字音时这样说:“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虔”字一字二音,照诚敬的意思读音为“前”,照掠杀的字义读音为“揭”。在这里读“揭”。骊靬,当地人自呼曰“力揭”,当地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我们不妨一试,念得快一些就是“力揭”,再快一些,就成“揭” 了。这样,骊靬县就成了“力揭”,骊靬人就成了“力揭人” “揭人”。怪不得当初王莽改骊靬县为揭虏县。于是“力虔”在演化中成为“羯”、“力羯”、“虔人”等。这些字,都是正统的读书人写的。因为是少数民族,就得写上带“羊”边的羯字了。《后汉书·西羌传》中,多处写到虔人羌,他们与其他羌族联合起来造反。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狼莫羌与虔人羌反,汉军在北地打败他们,“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指虔人羌一万一千人投降了邓遵将军。而《晋书》里对于羯人形象的描述更为具体,说他们“深目、高鼻、多须”(见《石季龙载记》)。“深目高鼻多须”的形状,正是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生理特征,也正是羯人即罗马人的人证。秦胡,即大秦胡的简称,有时叫秦胡,有时也叫大胡。在中国,东汉时期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后汉书》里写到秦胡的篇章有:
其一,东汉章和二年(88年),羌人反。羌豪迷唐率部与武威种羌万余骑,攻至塞下。护羌校尉邓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护迷唐于斜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这里,湟中指小月氏,秦胡即骊靬人。请注意,邓训是在凉州组织了这支军队,里面的秦胡来自凉州地区。(见《后汉书·邓训传》)
其二,同书《段靬传》记载:段靬是武威人也,从小就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好古学。做官就是武将。延熹二年,即公元159年,凉州有八种羌联合起来造反。朝廷任命段靬为护羌校尉,赴凉州去平叛。羌人起势凶猛,相继寇陇西、金城,以及河西四郡。并顽强抵抗汉军。凉州的秦胡骁勇善战。段靬率领以秦胡和湟中月氏为骨干的凉州兵,经十一年的战斗,才将羌叛平息下去。十一年,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建宁三年春,段靬凯旋回京,“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交给朝廷,请注意,武威人段靬部队中的秦胡仍然来自凉州地区。
其三,再看同书《董卓传》。董卓是陇西临洮人。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北地先零羌反,凉州的汉朝官员韩遂、马腾也相继跟着造反。大家知道,马腾是马超的父亲。他们杀了凉州刺史耿鄙,气焰甚盛。朝廷乃任命董卓为破虏前将军,任命一个叫皇甫嵩的官员为破虏左将军。皇甫嵩是凉州安定郡人。二人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平息了先零羌及韩遂、马腾的叛乱。董卓自恃功高,拥兵自重,朝廷调他到京城做大官,但董卓不肯丢掉兵权,借故不去,给皇帝上书说:“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董卓说,他想去,就是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及秦胡把他挡下了,他没办法,只好顺从。请注意,秦胡还是在凉州地区。
其四,我们再看《三国志》,在《武帝纪》中也具体写了秦胡。建安十六年(201年),西凉的马超与韩遂起兵反叛,洛阳大恐。马超离他老子的反叛隔了二十七年。老子的对手是董卓、皇甫嵩,马超的对手是曹操。曹操与之交战,开始屡屡受挫。
曹操说:“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他决定智取,施离间计。韩遂与曹操是老熟人,曹操要求和韩遂说几句话,于是在两军前,与韩遂寒暄片刻。后日,又相见。《三国志·注解》引用了《魏书》对这次相见的具体描绘:
“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惧。”
“可为木行马”,是说在前面架起粗木防护栏。这段文字,可以说写得绘形绘神,十分精彩。曹操的这一招也真灵,和韩遂说的不过几句随便的叙旧话,但引起马超怀疑,结果马、韩自相火并,导致失败。请注意,这些秦胡兵还是来自西凉。
上述文字,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写秦胡的仅有的篇章,也是所有史书具体写到秦胡的仅有的篇章。这些篇章明确告诉我们:秦胡就生活在西凉地区,是西凉生活的一个少数民族。这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秦胡到底生活在凉州的哪个地方呢?这里,就不能不讲到有名的卢水胡。说实话,对“秦胡”的概念,曾经有史学家做过另外的解释,但我们上面所举史实表明,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民族概念,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称呼。1976年,在张掖北部的汉居延遗址,发现两万多枚竹、木汉简,其中一枚上有六字“属国秦胡卢水”。属国指张掖属国。这句话说清楚,就是:张掖属国卢水地区的秦胡。秦胡生活在卢水地区。这汉简就是铁证。
而卢水地区又指哪一带呢?让我们走进《后汉书》和《三国志》所描绘的世界,里面的卢水胡会告诉我们:卢水就在骊靬县。不信请看:
其一,《后汉书·西羌传》说,建初二年(77年)夏,迷吾羌聚众反,“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说的是张掖属国管辖的卢水胡。很显然,卢水胡在张掖郡。
其二,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4年),汉明帝为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发七万兵力,从玉门关到雁门关这一条线上,分四路进击西域。《窦固传》中是这样写河西这一路的:“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胡,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很显然,这里说的卢水胡仍然在张掖郡。
其三,同书《邓训传》中说:“元和三年(86年),卢水胡反叛,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东汉光武时,武威郡治从民勤北迁到了姑臧。邓训是受命去平息卢水胡的。任务艰巨,情势紧迫,需快马加鞭火速投入工作。但这里,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乘驿车去上任的邓训,本应到张掖郡去当太守,怎么待在武威郡当起了张掖太守?其中究竟有何玄机?答案很明白,也很简单。因为出了武威西门,就是卢水胡的天下。姑臧以西是什么地方?是显美、骊靬、番和。反叛的卢水胡就聚集在骊靬一带,邓训只能在武威,实施他的平叛计划。很显然,卢水胡就居住在张掖郡的骊靬县一带地区,延及番和、显美。
其四,再看《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刚当上皇帝,卢水胡在伊健妓妾、治元多、封赏等人的领导下起兵造反,武威、张掖、酒泉的太守也率郡相应,河西形成割据之势。实际上这是河西人反对曹魏朝廷的政治起义。曹丕派镇西将军曹真率十万大军来镇压,又任命文武全才张既为凉州刺史,辅曹真军事。《三国志》对这次战争作了十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简要概括一下曹真、张既取胜的经过:(1)渡黄河从景泰直插武威、攻下武威,切断已攻到永登的卢水胡先锋后路;(2)诱敌深入,前后夹击,歼灭显美的卢水胡,俘虏万余人;(3)派新任的武威太守贯丘兴深入卢水胡大本营骊靬番和,说服卢水胡放下武器。书中写:“兴(贯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皆弃恶诣兴,兴皆安恤。”(4)安抚卢水胡后,迫使叛官张掖太守张进、酒泉太守黄华投降,河西遂平。此次平叛,历时二年,斩首五万余级,俘虏十万余,可见规模之大。请注意,《三国志》中这些文字,具体准确地告诉我们:卢水胡生活的大本营就是骊靬县,旁及番和、显美的一些地方。反叛队伍里当然也有不少汉民,但起事者头头是卢水胡人,书中只能概称为卢水胡。
其实,卢水就是今日的者来河。永昌地名普查时发现,当地老人仍把者来河上游叫早卢沟,即当年卢水河之意也。这就是明证:卢水就是者来河,它穿过番和,流入金川河。这就是卢水地区,万千异族生活在这里,按民族性讲,他们叫秦胡,按生活地域讲,他们叫卢水胡。汉简“属国秦胡卢水”,明确记载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自己疾呼曰力揭,王莽称他们为揭虏,提法又演化成羯人。
另外,《后汉书》还有两处提到卢水胡,一处是《西羌传》中,说:中平二年,烧何羌犯卢水胡,为卢水胡所重创,头人比铜钳率众去依附临羌县。临羌在今西宁附近。按此情判断,卢水胡重创比铜钳的地方,应该是骊靬县南山的北麓。再一处是《西南夷传》里提到的一句:“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黄石旧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北地即今宁夏吴忠市一带。这两地的卢水胡,是从河西东迁过去的骊靬人,缘由在后面细说。
在上面,我已向大家提供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具体写到卢水胡的全部文献史料,是忠实、直接地提供,没有断章取义,也没移花接木。之前的史籍中没有这个民族概念,以后,也只是在《魏书》中提到:北魏太平真君六年,一个叫盖吴的卢水胡人,在陕西杏城领导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自称天台王,最后失败。我想,任何人只要他忠实于那些历史文字的叙述内容,都不会作出另外的判断。
晋代,骊靬人在武威郡叫骊靬戎,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晋书·张祚传》中的有关记载。该传说:永和十年(354年),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晋代,骊靬县属武威郡。张祚在武威自立凉王,骊靬戎不服,揭竿起义,并打败了前来讨伐的和昊将军的部队。公元22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是卢水胡,时间过去130年,在骊靬县聚众造反的又是骊靬戎,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恰好说明,卢水胡本身就是骊靬人。
好了,我们以时间先后做排列,做个小结看看骊靬县居民称呼的演变情况:
公元前48年一前45年,骊靬建县;对骊靬,当地居民疾言之曰:力(虔)揭,自呼曰:力揭人;公元8年,王莽改制,称骊靬为揭虏;公元88年,邓训在西凉发湟中月氏、秦胡、羌兵四千,出击迷唐;公元201年,马超率西凉秦胡反;公元74年,窦固率张掖属国卢水胡出征西域;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公元221年,武威太守贯丘兴到骊靬县和卢水胡谈判;公元354年,骊靬县的骊靬戎打败张祚的讨伐部队。结论:在中国的古罗马人叫骊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又被称之为揭虏、力羯、羯人、虔人、秦胡、大胡、卢水胡、骊靬戎等。
至此,我们不能不请出两位骊靬人皇帝和大家见面。他俩是谁呢?他俩,一个就是羯人石勒,另一个就是卢水胡沮渠蒙逊。前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赵,后者,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北凉。
石勒,山西上党武乡羯人,即骊靬人,字世龙,又名匐勒。有勇略、善骑射、自幼常代父亲掌管部落事务,为众所服。西晋太安中被晋军掠卖山东为奴,与一个叫汲桑的人聚众起义,一度攻取邺城,后兵败,投汉国刘渊为将,作战有勇有谋,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权位日重。大兴二年(319年)自建政权,号称赵王,史称后赵。据有冀、并、幽州及辽西一带。公元330年称帝,改元建平。在位期间,删减律令,立朝仪核户籍,定祖赋,兴学校,于诸郡立学官,办了不少好事。
沮渠蒙逊,张掖郡临松卢水胡人,也即骊靬人。其祖先曾在匈奴做过官。沮渠蒙逊初为后凉吕光部下。《晋书》说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才有英略,滑稽善权变,甚为吕光所器重。公元397年,叛吕光自立政权,史称北凉,据张掖,自称张掖公,改元永安。永安十二年,迁都武威,改称河西王。寻继灭西凉,占有西凉七郡,界连西域,在位32年。
六、古罗马人过黄河
既然卢水胡的家乡是骊靬,卢水是骊靬、番和一带,为什么黄河以东也出现了卢水胡,如北地卢水胡、杏城卢水胡?山西出现了羯人?道理很简单,河西骊靬人即中国的罗马人,到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发生过几次东迁的事,这是因为发生几次重大军事行动,简而言之,主要是:第一次,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西征魏嚣,时为河西大将军的窦融,率河西数万汉、胡步骑,以及辎重五千余辆,过黄河拜光武于高平(今固原),联合击败魏嚣,并将军队交给光武帝。窦融被封为安丰侯。这批投入光武帝统一大业的河西兵(自然有不少秦胡),战争结束后被安置于河东。
第二次,窦固征西域,率张掖甲卒及卢水胡出酒泉塞,战争结束后,部分被带回洛阳。
第三次,建宁三年春(170年),段靬率西凉五万秦胡步骑及汗血千里马回洛阳。
第四次,董卓讨平羌叛之后,被认命为并州刺史,他不放兵权,并把这支有骊靬人在内的西凉兵带到了山西,后被召入京,他又把部分西凉兵带入京城。
第五次,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韩遂反叛,带领以秦胡为骨干的西凉兵与曹操大战于潼关,最后曹操击败马、韩,并将俘获的西凉兵编入自己的部队。
第六次,三国黄初元年至三年,骊靬卢水胡反叛,镇西将军曹真率大军西征卢水胡,最后卢水胡败,曹真带十万俘虏回洛阳。
这六次,都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这些随军而东的西凉兵,年高退役后,基本就地安置,在那里繁衍生息,于是那里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即羯胡、卢水胡。
七、金关汉简告诉给我们什么
汉代有名的居延海在张掖以北,现在这里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汉代,这里是重要的边防关塞。1972—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两万多枚汉简。简册内容广泛,涉及汉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以屯戍内容为多,且保存了一部分汉代官方文献。这批简,又被称为居延金关汉简。已确定,它们在被埋时已经十分散乱,出土以后,年代及内容也颇多错乱。《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4版,公布了汉简中涉及骊靬内容的13枚,到底如何解读,还需要商榷。这13枚简,现全部抄录如下: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
简三:“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
简四:“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
简五:“□出钱五十,栗五斗,骊靬。”
简六:“靬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
简七:“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
简八:“出栗二斗四升,以食骊靬单门安。” 简九:“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
简十:“□过所遣骊靬禀尉刘步贤□。”
简十一:“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
简十二:“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
简十三:“骊靬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上列汉简,乍一看来,确实有点叫人眼花缭乱。有人看到简一中“神爵二年三月”六字,便啧啧说道:“骊靬建县与古罗马人无关,因为神爵二年已经有了骊靬县,神爵二年是公元前60年,古罗马人侵安息的卡莱战役发生在公元前53年。”
但是,请看清楚一点,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简文,毋庸置疑地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苑、县有天壤之别,前者是马场,后者是行政建制,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人一生的照片,放得无论怎样错乱,仍然能够从体貌上分辨出时间段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分辨出上列汉简的时间段。
如果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惊人的现象:它们清楚地分为骊靬苑、骊靬县两大类,凡是记录苑的,都牵连着番和县,凡是记录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苑内的工作人员,必然来自番和县,凡在县衙服差的,都和番和县无关;凡涉及苑的村庄,都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涉及骊靬县的村庄,也都和番和县无关。对苑、县的记录是如此泾渭分明。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清楚:苑跟番和脱离不了联系,是因为苑本身就设在番和县境内,所以勤杂人员必然也只能来自周围的番和县村庄,作为马场的骊靬苑不可能有自己的行政村;骊靬县跟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骊靬苑已从番和境内分割出来,以县份的面目出现,有了骊靬县自己的行政村,所以其当差人员不是来自番和而是来自骊靬本县。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无须假设,也无须估算,和骊靬有关的13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清晰地呈现出它们的真面貌。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属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简一、简二、简十一、简十二、简十三五枚,为一大类,属于骊靬苑时期的文书内容;简四等另外八枚,为另一大类,属于骊靬县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时间在前,骊靬县时间在后。前者表明,骊靬苑设在番和境内,故啬夫、杂役、牧奴等固然都来自番和,负责人为苑监;后者表明,从番和分割出来的骊靬县,以行政建制独立存在,人员再不需要从番和招募,自然要从骊靬本县的行政村招募来。负责人为县长。
有“神爵二年”字样的纪年简面目也清楚了,神爵二年为公元前60年,它明确告诉我们,此时只有骊靬苑,没有骊靬县,此简是骊靬苑时期的。换句话说,它明确告诉我们:公元前59年之前没有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的某年,骊靬神秘地以行政县的面目出现了。
西汉王朝为抵御外侮,在西北边郡建立养育军马的牧苑三十六所。祁连山下,番和之地,有丰富的草场,在番和境内建立马场,合情合理。之所以将番和的马场取名为骊靬苑,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之处。一则,骊本义就是黑马;二则,也许专门养育的是来自西域的胡马,故名;三则,也许体现西汉皇帝对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番邦的向往,故名。但问题是:为什么骊靬苑突然变成了县?为什么建县以后仍然坚持这个对人不尊的名字呢?而且,《汉书》告诉我们:西汉建县有一条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还为什么从民稀的番和县内切割出蕞尔之地另建起一个县呢?显然,其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不建置骊靬县,就不能最妥当地处理当时的特别事件,究竟是何特殊事件?这就是公元前48年至前45年之间,数千流亡在中国西界之外的古罗马士兵归顺西汉,他们正好来自遥远的骊靬国,番和县正好有个骊靬苑,这里过去是折兰王府,现在又是牧苑,设置条件具备,所以正好可以把这批人安置在这里,建县以领之,名字也无须改了。这不是“说曹操曹操到”,太有点巧合了吧?其实,无巧不成书,整个历史就是由无数巧合构成的。偶然构成必然。历史上“说曹操,曹操到”的事件还少吗?正是番和境内有个骊靬苑,后来归顺的骊靬人被安置在番和境内另建县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作者于2006年4月14日下午金昌市党校小礼堂做讲座。此稿是作者于2007年6月根据讲座稿整理而成。)
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
王萌鲜 宋国荣
古骊靬县的建立,与陈汤俘获的那批“战俘”有关,此说,引起部分史家学者的质疑,是无可辩驳的史实。但骊靬县确为一批古罗马人而特例建置,却也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和一些历史学家的探讨,论证如下:
第一,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中国的一批权威史书,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还指出: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第二,为骊靬降人设县有据可查。《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靬说:“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师古之解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所以如此,就在于它的可靠性。师古也许料到会有人怀疑他的注释,特地向后人交代说:他的注释“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师古语)。其实,早在以前,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这“蛮族”即骊靬人。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诂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涉足骊靬者不乏其人,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靬县取骊靬国名为县名,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中国从汉、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应、颜之说,“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只是由于典籍的大量失传,我们无法看到他们考证时所根据的材料。如徐松、为嘉庆编修,因坐事戍伊犁,致力于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北史地的研究,破疑解难,成绩卓著,为世所公认。现在有人武断地说这些学者结论没有根据,未免过于草率。现在还有人说:颜师古之解始于初唐,跟西汉中期六百多年,不足为凭。如果时间能够成为理由,那么,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距西汉两千多年,距初唐1400多年,更有何资格去评说或否定颜师古搞错了呢?正因为历史遥远,大量资料在不断遗失(这一点只要看看《汉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书目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就是凤毛麟角,如同长夜里的一盏小灯,只能守护,不能把它扑灭。因此,不能否定中国从东汉初唐到清末一批学者对骊靬研究的成果。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若干现代学者在这块土地上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不仅信心十足地坚持了应劭、颜师古之说,而且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前者如向达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后者如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
第三,确有大批古罗马人生活在河西。这批古罗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靬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靬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如《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189年),朝廷徵卓为少府,卓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腹上。”这里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就是湟中羌和大秦胡之意,后面的“羌、胡”就是“湟中义从及秦胡”的概语。秦胡确指古罗马人。有人认为,此处“秦”指汉人,假设如此,那么,下句的“羌、胡敝肠狗态”作何解释?汉人到哪里去了?再如,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曹操施离间计,约韩遂“叙旧”,以引起马超疑心。《魏书》具体记下了会语的情景。《魏书》说:“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防护木栏)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这《魏书》是曹魏朝廷编撰的皇家史,成书早于《三国志》,现在我们无法看到曹魏《魏书》,但这段文字却由南朝的裴松之抄录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注释中,十分可贵。这段文字,“胡”出现两次,前面点出是秦胡,后面就省掉秦字,正好说明“秦”是对该胡属性的限定。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有“属国秦胡卢水”的记载,“秦胡”纯属为民族之称,证据充分。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西汉初个别情况下也确称汉人为秦人,但秦人和秦胡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是两个概念。古史书中将汉人和少数民族并论时,总是讲“华夷”或“夏夷”,从未有过“秦夷”之称。那种把“秦胡”认为是汉、胡之合称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元人胡三省在解释《通》东汉章和二年邓训部中的秦胡时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此话大谬,章和二年,此时,建汉已三百年,历十二三代人之久,有什么秦威遗存?钦定的《后汉书》、《通》的著写者,又怎能以夷人口吻写史?秦胡即大秦胡,即古罗马人,实在没丝毫含糊处。
因为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靬人又称作卢水胡。骊靬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延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意即旧时之卢沟。《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靬、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靬戎造反之地。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因为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靬戎。《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靬戎”者虽属绝无仅有之笔。虽少,却实乃为铮铮发光,一字千钧的文字,须引起任何一个史学家的直面。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上确有数以万千计的被称为“秦胡”、“骊靬戎”或“卢水胡”的罗马人在河西生活。尽管他们在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本营却只有一处,即以骊靬县为中心,旁及番和、显美、临松县这一地区,即卢水地区。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第四,河西罗马人来自克拉苏东征军实属必然。西汉时期,中国跟罗马不存在商贸往来。甚至罗马使者也不能通达,自然谈不上罗马商人入汉。原因就是安息阻隔。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的:“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丝绸)与之交市,故庶阂不得自达。”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才有首批大秦使者到中国。那么,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答曰: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为争夺商业和领土,克拉苏发动了对安息的战争。通说克拉苏率五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1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一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14卷)。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 北靠康居, 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来往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响彻昼夜。那些在战场上逃逸的罗马士兵,以及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不堪忍受安息人欺辱的罗马俘虏,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从商道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靬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缘由。
具体完成这一重大行动的人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为陇西狄道人,仕途阅历并不复杂。少时随长罗侯常惠将军屯田乌孙赤城,汉元帝初,举茂材,拜为朝廷郎中车骑将军,寻迁张掖太守,时为初元元年(前48年),八年后迁酒泉太守,因“在两郡著功迹”,成帝初(前32年)征为朝廷光禄大夫,后为光禄勋,元延元年(前12年)去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班固在传中作了这么一段记述:辛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 此处的“西域亲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西域乌孙国时,不过是常惠部下小卒,无关轻重;后为光禄大夫时,管的是顾问应对之事,与西域无关,西域事由典属国掌管。辛庆忌到底是怎么在和平年代而使“匈奴西域亲附”的,答案就在张掖太守中。从时间推算,辛庆忌在张掖、酒泉两郡待了十六年,他在张掖的任期至少是八年,即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0年。《汉书·辛庆忌传》中说他在当车骑将军时“尚未知名”,而迁张掖太守后即“所在著名”,正是他作为朝廷的和平使者,奉命从西域大月氏等地接回要求内迁的罗马流亡军人,安置在他所管辖的番和县南照面山下。以此义举而扬名天下,而成为国家虎臣。从此,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使后人扑朔迷离的县:骊靬县。
第五,居延简的历史回首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有关骊靬的十二枚,尽管纷乱无序,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一惊人的历史现象:
凡是记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记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骊靬县的村庄,又都和番和县无缘,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后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角乐得□□,骊靬常利里冯奉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兒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前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0年以后才出现的。
以西域的地名命名的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内以牧养西域进口的良马为主的国家牧场,地点在番和的城边。人们要问:为什么养马场在公元前50年以后某个时间突然变成县的建制呢?西汉立县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希则旷。” 为什么突然又在“民稀则旷”的番和腹地又另建县城呢?县城又为什么一定要以骊靬二字命名呢?为什么秦胡、卢水胡、骊靬戎偏偏一直居住在此地呢?很明显,建骊靬县,有其因时性,有其特殊性,还有其神秘性。它告诉我们:公元前50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附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谓骊靬人的古罗马人作为一个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靬县并入番和,骊靬存县600余年。
现在,有一个问题使学者们争论不休,即公元前36年,陈汤在对西域郅支匈奴讨伐中所获俘虏里到底有没有罗马流亡军人。这,只要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明白了。根据《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告诉我们的事实:郅支匈奴因屡杀汉使,深怕汉军联合南匈奴消灭他,便合众西迁,至坚昆;时康居国屡为乌孙所困扰,无力自卫。康居国王闻讯郅支西来,派使者至坚昆,答应给郅支在康居东边提供领地,欢迎郅支去驻,目的是将郅支作为屏障以胁乌孙。郅支大悦,移众继续向西。不料中途遇大风雪,数万之众死者十之八九,到康居东,苟活者才三千人,且伤兵者多。三千疲惫之旅,如何抵挡乌孙!郅支向康居王“借兵”,康居王借给郅支了一批人。这就是《陈汤传》中写的“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我们须特别注意“借兵”二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拥有六十万人口之众的康居不能自卫,郅支却靠从康居借来的“这批人”连续大败乌孙,致使乌孙胆寒,不敢西顾;不仅如此,郅支又乘胜骄,靠“这批人”反戈一击,一下子打得康居七零八落。郅支威震西域,成了一霸。“这批人”俨然如同神兵天降。很明显,这是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问题来了:“这批人”在康居那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又向康居反戈一击呢?我们可以断定,“这批人”在康居那里被视为异己,不受重用,为无用之徒,甚至受到歧视;而到郅支这边,疲惫中的匈奴自然要把他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力量。在康居那边他们是寄人篱下的睡狮,在郅支这边他们是腾跃下山的猛虎,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精通战术的战斗部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从安息西部草原上逃跑出来的克拉苏第一军团的部分,几经辗转而投靠康居。他们被借转而成为郅支匈奴的成员,并在后来参与了跟汉军的作战,形成罗马军人跟中国部队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触。首先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中国学者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提了出来。
有人说:“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已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 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克拉苏被重重包围,儿子为护父率军冒死突围在情理之中;克拉苏被俘,儿子为救父战死沙场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军团长战死,必有副军团长继任指挥,副军团长战死,必有另外的副手或下属继任指挥。这也是必然之事。“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显然是一句臆想之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大历史学家阿庇安告诉我们的:罗马军在卡莱战场上突围出了近一万人。为了活下去,这一万人必然要寻机奋力逃出安息,而较为松弛的安息东北边境为他们提供了出界的可能。何况安息首都泰西封就有商贸大道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陈汤俘获的匈奴中确有一批罗马军人。
无可否认,正如《汉书》记载,陈汤所获俘虏全部“赋予城郭诸国”。但《汉书》并未说这批俘虏就全部老死在那里,一直未做任何迁徙。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就可便知,古代环境为一个民族成批迁徙所造成的随意性和频繁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动辄南迁北移是常事。“赋予城郭诸国”的匈奴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断言他们就没有进入玉门关。他们跟骊靬县的建立无关,但却跟骊靬县的县民有缘。公元前48年前后,骊靬已在祁连山下拔地而起。
至于拿出个人对于“重木城”和“鱼鳞阵”的解释为根据,来否定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的部队同汉军作战的历史发现,更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说:“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这是一种臆想妄断。其一,不要忘记,公元64年毁于一场大火的罗马城,房屋基本上是用木料建造的,后建的新城才用石料取而代之,何况筑郅支城是公元前36年前的事,怎么能断然说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其二,倒退一步,就算是罗马军队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但是用兵之道,因势制宜,在彼处修石城者,不能说在此处不能修木城,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态势,罗马人协助郅支单于建造重木城并非天方夜话,惯于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穿起西装打起鲜艳的领带。我们大可不必为罗马人修重木城大惊小怪。
“否定论”者又说:“《陈汤传》中的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这又是一种妄断。他们解释说:“罗马乌龟阵是这样一种阵势。即军队进攻尤其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 这种解释,不攻自破。郅支单于的罗马人出于守城的需要,自然主要将盾牌挡在前面排成鱼鳞阵,演习防守的阵形,不需要“将盾牌高举过顶”的攻城阵形,因为他们眼前的形势是防御。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作战阵形主要承袭古希腊的作战阵形,以战士密集成列的方阵为基本形式,为着作攻防要求可以随时变换其形状。卤盾举过顶形成“乌龟壳”,或者卤盾不举顶而排成鱼鳞状,都是因不同需要而出现的形式变换,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拳击运动员出拳,出左手和出右手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硬要加以区别,而且是本质的只能使自己陷入荒唐。
至此,正如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辞海》在骊靬条目中诠释的那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在今甘肃永昌南。”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罗马城是为古罗马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古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
骊靬故县与罗马降人
宋国荣
骊靬,是西汉时期设在今永昌县境内的一个故县。有关骊靬县的设置,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多有记载和注解。唐初学者颜师古(581—645年)《汉书·张骞传》注解中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晋书·张祚传》载凉王张祚“……永和十年,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后汉书补注》、《二十五史补编·新斛地理志集释》、《大秦一统志》、《甘肃通志》、《乾隆府厅州县志》、《凉州府志备考》、《永昌县志》记载略同:“盖骊靬国人降,置此县以处之也。”“今凉州府永昌县南,本以骊靬降人置县,者来寨是其遗址。”1936年,中国首部《辞海》,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马部骊靬条均说: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在今甘肃永昌县南。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即此。《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按《隋志》开皇中并力乾县入番和,当即此县。”
清代学者惠栋(1697—1785年),在其著《后汉书》补注中说:“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王先谦(1842—1917年)在《汉书补》、《后汉书集解》中说:“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治经史,精于西北地理之学的张穆(石州1805—1849年)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嫠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钱坫(1744—1806年)、徐松(1781一1848年)、王筠(1784—1854年)等清代经史学家,考证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
1920年,史学家向达(1900—1966年)在《中外交通小史》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①中说:“汉代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又称之为犁靬,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别名。”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而汉时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之盛,于此也可概见。”1944年,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冯承钧在其著《西力东渐记》①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②所录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1907—1980年)《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提到公元前36年陈汤伐郅支时说:据现代学者考证,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北匈奴郅支单于既死,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遂统一匈奴。有关研究骊靬的历史学家和著述还有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1902—1987年)的《汉张掖郡骊靬县的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③;西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宗维(1934一)《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④;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毓棠(1911—1985年)《汉代的中国与埃及》⑥;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常征的《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件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⑤;法国学者L.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⑦;美国历史学家罗兹的《亚洲史·中国文明·中国和罗马帝国》等。他们都论证:骊靬县的设置与骊靬人来华有关。尤为张维华他在《汉张掖郡骊靬县的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中否定了自己前期著《骊靬县得名之源》⑧一文中提出的“骊靬为祁连译音”之说后说:“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现代史学家史念海在所著《河西集·河西与敦煌》中记述:“骊靬为县名,当是因骊靬降人而设置的。以域外降人设县,亦见于上郡的龟兹县,其县也是因龟兹降人而设立的,这在汉时已是通例,无足为奇。”
从上述历史经学家和学者对骊靬的解注中看出:骊靬县的设置是为安置从西域归降的骊靬人而设,古来就有记载,是有传承性的。并不是今人的所谓发现。
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谦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古代中国之骊靬城》,当时应历史条件的制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9年,时在甘肃省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通过法新社在新华社《参考消息》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一文(见1989年12月15日)。同月3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内容更详细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许多媒体和学者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但,这里并没有发表哈里斯等人学术上的任何东西,为此,学术界持根本的否定态度。
缘由是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等学者研究认为:公元前54年,古罗马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4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安息(今伊朗东北),第二年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克拉苏被杀,只有部分军团士兵突围逃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尔莱战役。这些逃出突围的罗马人后来流落到西域的乌孙、康居等国做扉佣军。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联合康居、乌孙等西域15国兵讨伐匈奴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发现一支奇特的部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他们认为,这里的“鱼鳞阵”和“重木城”只有罗马军队采用。而这些使用“鱼鳞阵”和“重木城”的士兵就是克拉苏兵败后逃亡西域,后来依附匈奴郅支做雇佣兵的罗马士兵。这次战争汉朝军队获胜,西汉政府便设了骊靬县来安置这批罗马战俘。
十余年来,永昌的骊靬古县,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专栏于2001年7月15日,在永昌骊靬村作了现场直播。中国的香港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甘肃电视台,还有西班牙、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外的电视台都来永昌拍制过有关骊靬的专题片。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德国的《镜报》、波兰的《共和国报》、法国的《欧洲时报》等中外百余家报刊对永昌骊靬古县和骊靬降人进行了报道。
骊靬古城为罗马战俘而设,也就是与甘延寿、陈汤俘获的战俘有关一说,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因《汉书·陈汤传》中记载,汉军伐郅支匈奴所俘获的千余战俘都“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根本未被汉军带入玉门关,跟骊靬城的设置没有关系。为此,一些学者根据新闻报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提出质疑和商榷的观点。其主要有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对此说有感而写的散文《天涯何处骊靬城:读书献疑》①,北京大学教授杨共乐的《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德芳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②等,学者们通过研究史料对骊靬城与罗马战俘的关系提出质疑和否定。
近年来,虽然人们在骊靬上热情不减,但争论的焦点还只是一个“古骊靬城与骊靬降人是否有关”。其中存在的疑点还需要有关专家学者探考研究和商榷。如果把学术界、媒体报道中的一些人和事,拿来做否定骊靬县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理由和论点。显然是不妥当的。
骊靬县与骊靬降人,在历史上千百年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汉唐时期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会点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具体反映,它对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往,中华民族的发展形成,彰显中华大国文化深厚积淀的强大包容性和独特人文魅力,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永昌经济社会,提升地方知名度,开发旅游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价值。研究和保护性地开发骊靬,不但是永昌县的大事之一,更是甘肃省的一件大事。
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研究
刘继华
德效骞,英文名为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于1892年3月28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Deerfield),是近代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早年跟随父母来华过颠沛流离的传教生活,青年时出于宗教热情来华当过基督教传教士,并出于传教目的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从此走上汉学研究之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 Chicago)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马歇尔学院(Marshall College)、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ofLearned Society)、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及其神学院、太平洋学会(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中研究汉学,在汉学界声誉日隆,最终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①,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他是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最早提出者,因此要厘清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渊源,他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本文对他的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推进骊靬文化研究的开展。
德效骞首次提出罗马军团来华说的时间为1940年,而不是许多论著所言的1957年。在1940年,他在杜克大学及其神学校任教,于著名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了《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AMilitaryContactbetweenChineseandRomansin36B.C.”)一文。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与另一位教授的研究有关,这位教授是荷兰汉学家戴闻达。
一、戴闻达与德效骞关于郅支之战的讨论
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一1954年),1889年出生于荷兰哈灵根(Harlingen,Netherlands),起初在莱顿大学学习荷兰语文学,不久跟随因著有六卷本《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而闻名的荷兰汉学家、人类学讲座教授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年)学习汉语,1910—1911年在巴黎又受教于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年)、高迪爱(HenriCordier,1849—1924年),奠定坚实的汉学基础。他于1912—1918年来华担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翻译,1919年在莱顿大学作为汉语讲师开始学术生涯,1930年成为莱顿大学教授,并成立汉学研究所(SinologicalInstitute)①。他因翻译《商君书》(TheBookofLordShang)和研究《道德经》而闻名,曾担任《通报》的共同主编(coeditor)②,为荷兰汉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戴闻达于1938年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十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西汉史上一次有插图的战争记载》(“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inthe 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③,该文对《汉书》中所记载的郅支之战进行了翻译,并进行了解释。该文经过充实、修改后,于1939年发表在《通报》上。这篇文章引起德效骞关注,他认为戴闻达推断出陈汤带回他进攻单于城市的图画,并且这些图画在皇帝的宴会上引起浓厚的兴趣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存在陈汤应该有描绘自己获得大胜的图画许多理由,比如陈汤有矫诏出兵之罪,他必须尽可能地取悦皇帝和宫廷以减轻罪责,于是他将图画与他的报告一起呈送朝廷,而这些图画可能会取悦于朝廷。德效骞认为在古代行军中,中国将军进入未知疆域存在绘制地图的事实,并以李陵带兵征讨匈奴为例。
当他(李陵——引者注)前行(在他被匈奴攻击之前)时,他对旅行过的地方绘图。文献(《汉书》卷54)说当他到达他的军队进入匈奴疆域最远的地方,“他停止,扎营,在地图(图)上记录山水和所经之地的构造。他派遣麾下骑兵陈步乐回(到汉人地界)以便(后者)可以报告(给武帝),送这些地图。步乐(然后)被皇帝召见”④。从这段记载,似乎制图是武帝及之后远征军的一项一般性项目,为此中国将军带着会画图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画家。如果制图是中国远征军一项公认的功能,被陈汤送回的图画的制作者可能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另一事件似乎证实这一假设:陈汤的军队没有在康居人的疆域浪费时间,而是直接进攻单于。康居人表面上敌对,因为他们与单于结盟,以至于陈汤不得不用俘获那些前来引导他的人为借口,来说明他们出现在他的军营。郅支单于已经因其横暴而得罪许多康居人,所以他们想帮助中国人,但因为他们的联盟,他们不敢公开这样做。因此在战争前极不可能的是有一个康居人在中国军营。他可能在后面跟随,但他几乎不可能画这场战争。①
从上述引文可看出,德效骞得出制作地图是汉武帝及之后中国远征军经常性的事务,由此进一步推导出,陈汤军中的画师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并以康居人因与匈奴结盟为依据证明康居人不可能是反映郅支之战图画的制作者。他认为古代中国地图上有反映地方情况的图画,由此提出从中国到康居的地图一定是一张长卷,而在两边则有许多空白之处,对这些空白之处,他认为画师会用汉军进攻郅支单于的景象来填充。
一张长途的画,从中国疆域到康居,一定是张长卷,有许多空白地方在两边,代表遥远的路途。对于一名画家而言,自然会用对单于城的辉煌进攻的激动人心的景象来填充一些空白地方。一个令人想起的例子是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他年轻时在美国政府服务,他镌刻的地图上刻上了海鸥(因此他被解雇)。因此这些地图成为陈汤送给朝廷报告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图画,当然这些图画引起家里人和宫廷妇女的关注。② 利用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的事例,他推导出画师会在地图上画上郅支之战的情景,由此陈汤上报朝廷的地图上有反映郅支之战的画,这些画引起国人和宫廷妇女的兴趣。接下来,他对戴闻达使用的一个短语提出质疑。
你(即戴闻达——引者注)翻译中的一个短语,我大胆挑战,特别是因为它加强你对图画的假设。在第259页第9行,在描绘单于门外步兵的地方,你翻译为:“lineduponeither side of the gate ina formationascloseas thescalesof afish.”在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 closeas”。我认为宁愿用“afish-scaleformation”。我由它想到希腊人重叠盾牌的行为,这叫作过度防护(Over-shielding)。这样一个战争排列自然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对他们来说它是陌生的。康居人可能从以前征服他们的希腊人那里学会它,特别是因为它曾有效地打击自己。这样一种排列无益于反对中国人的强弩,它能射穿任何盔甲。画家看见这种阵势将会把它带入画中,作为他注意到的奇异风俗的一个典型。在另一方面,它不可能进入书写的报告,因为它对没有见过它的中国人没有意义。因此这个短语“鱼鳞阵”很有可能来自一幅画而不是来自报告。我想知道如果陈汤地图上的图画不是严肃的雕刻:一系列小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分别被边界隔开,以致该系列给予战争的一系列场景。然后这个新的特征,如果有的话,在一个组成的画中对一个复杂的事件不做如此多的分析,而只是一系列画,组成一个连续,去讲一个故事,像ChinMi-ti下跪的情景和同样的人渴望地看着雕像(你的第253页底下的第4个注释)。画家自然以这种方式看一场战役。你的记载将组成半打图画。
① 他认为中文中没有词表达“ascloseas”,用“afish-scaleformation”即鱼鳞阵更适合原文的意思,并将鱼鳞阵与希腊人的叠盾行为相似,认为这是征服过康居的希腊人留给康居人的影响,而这种阵势无法抗击中国强弩的进攻,但却作为奇风异俗而引起中国人的注意,鱼鳞阵来自画而非报告。他认为陈汤地图上的画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讲述着郅支之战的故事。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所作的评论非常重要,接受了他关于图兼有图表、图画双重意义的说法,认为这比自己的本来想法更具说服力;同意德效骞所提出的古代地图上会在相关地方添加图画予以注释的意见,认为反映郅支之战的六幅画是一个系列,一起说明郅支之战的故事发展进程。
德效骞博士的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在这个图中确实更像兼有图表和图画的意思,这甚至比我起初的想法更令人满意。我们的古代地图不反对在它们上面对地方添加图画般的注释。我非常同意这些图画组成一组,一起说明故事的发展。这是我在论文中的意思即使我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这个意思。它们被边界隔开或它们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合成物,多种元素显示事件的连续发展。我们没有方法知道。德效骞教授的建议即步兵的鱼鳞阵势可能与希腊风格的阵法复合盾有关是特别有价值的。然后这些步兵一定是康居人而不是匈奴人。这是希腊对该地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证。②
戴闻达认为德效骞提出的鱼鳞阵与希腊风格的复合盾阵法相关的想法非常具有价值,这是希腊文化对康居地区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当然,戴闻达并非完全赞成德效骞的想法,他认为画师不一定是中国人。不过他不会计较于画师的国籍,他认为“不管画师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幅公元前35年存在的画的事实是不同寻常的重要,它与编史的联系依然非常重要”③。
二、德效骞的《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
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据其自己交代,目的有二:一是为戴闻达教授关于郅支之战的研究提供佐证,二是更正自己之前对这场战争所发表的评论。
他在文中首先提出应该注意研究描述郅支都城的防卫者的特定词组,《汉书》中“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中的“鱼鳞阵”一词自然会提出关于能够摆出如此复杂阵势的军队的类型及其国籍的问题。
我(德效骞——引者注)提出特别的短语来研究郅支首都捍卫者的描述。中文记录描述“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现在“鱼鳞阵”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物,它自然引出关于能执行如此复杂军事策略的军队的特征和国籍问题。这些士兵必须制定这样一种方式,以便他们挤在一起并且将他们的盾重叠在一起。成功地完成这一壮举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这样有序的事情不是与匈奴一样的任何游牧民族所能够办到的),意味着较高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在这些士兵身上可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训练。牧民、蛮夷和高卢人一样混乱地冲进战争;鱼鳞阵的方式需要纪律和训练;只有职业士兵在面对攻击的时候才能成功地运用它。①
他认为鱼鳞阵是个非常复杂的阵法,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需要经过较高文明教育的士兵,而且这些士兵需要经历长期的军事训练,由此他提出这个阵法所需要的纪律和训练不是匈奴等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游牧民族不具备实践鱼鳞阵的条件,只有职业士兵才能运用它。那么职业士兵的国籍是什么呢?
我(德效骞——引者注)首先猜想这种阵势是陆龟或龟,罗马人常用来攻克堡垒。他们将盾举过头以保护他们免受飞弹落到他们身上。但是都赖水距离任何罗马领土都非常远;它在咸海东部,大约在东经71。北纬43°。即使Praaspa,公元前36年在安东尼的领导下,罗马人突破的最远的东面距离仅在东经46°。在中文记录里没有进一步提到盾在士兵头上。因此我得出结论,自从希腊人征服康居,这些士兵必定是希腊人。所以我被误导了。②
德效骞在思考鱼鳞阵时,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士兵在进攻堡垒时所用的龟甲阵 (testudo),但郅支城在都赖水旁,距离罗马帝国领土遥远,由此他排除了罗马
① HomerH.Dud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4-65.
②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p.65.
人而认为是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的可能性大,他们曾经征服康居,但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成立,并提出结论不成立的原因。
但是希腊人的大夏(Bactria)在公元前141年和前128年之间,很可能在公元前130年,大约在陈汤远征之前的一个世纪,被蛮夷打败。此外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明白在那个时候(鱼鳞阵)与马其顿方阵或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有什么关系。这或许意味着方阵在康居持续了一个世纪……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马其顿方阵扛着小的圆形盾,这使得人们无法紧密地拥挤在一起,不能出现“像鱼鳞那样排列”。①
结论不成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所建立的大夏在陈汤远征前的一个世纪即已灭亡,而且在塔恩(W.W.Tarn,1869—1957年)博士给德效骞的来信中,说明“任何希腊方阵的想法似乎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希腊人所拿的小型圆形盾无法使人紧密地站在一起而形成鱼鳞阵势。这样他就改变了之前关于鱼鳞阵来自希腊人的看法。然而塔恩博士在信中提到了公元前54年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士兵,从而让德效骞将鱼鳞阵的运用者重新回到了罗马人。
塔恩教授也亲切地指出,公元前54年克拉苏战败后,奥罗德斯二世 (Orodes Ⅱ)将他的罗马战俘安顿在马尔吉亚那(Margiana)(包括目前的木鹿),以守卫他的前线。一万名战俘有多少人到达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Carrhae)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们在这样的行军中难以得到善待。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娶了蛮夷妇女为妻,并在帕提亚军队中服役。有个故事,公元前36年,安东尼(Antony)在撤退时,得到克拉苏军队的一位幸存者警告和指导。他一直服役于帕提亚。这个故事不真实,叫这人为Mardian的来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但是维勒尤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和弗洛鲁斯(Florus)认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事实或许意义重大。
这些罗马人到达马尔吉亚那后做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他们曾经是军队,靠打仗谋生。希腊人、萨卡(Saca)人和其他人习惯做雇佣兵谋生。
罗马人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罗马国家能够吸收所有罗马人作战。克拉苏的人因遥远的距离和带有敌意的帕提亚人而从罗马领土分离出来了。唯一自然的是,或许这些罗马人中的一些人在机遇到来时,可能会以雇佣兵谋生。
从帕提亚边界、阿姆河(Oxus)上的马尔吉亚那边界到都赖水上的郅 支都城大约有400至500里,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郅支城前人们像鱼鳞阵一样排列的时间相距有18年。如果这是罗马人的阵势,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有来自克拉苏军队的罗马军团士兵。①
德效骞综合其他学者的说法,认为卡莱战役中战败的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国王安顿在马尔吉亚那,推测他们到马尔吉亚那后会以雇佣兵为生,并认为如果《汉书》中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那么其运用者肯定是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军队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那么鱼鳞阵是罗马军队的阵法吗?德效骞认为“似乎只有罗马军团的长方形盾的武器和面对弓箭罗马人的锁盾排列能称得上鱼鳞阵”,但罗马人的阵法无法对付中国人强劲的弩箭。
当中国人进入郅支城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首先在远处用弩火箭攻击该镇。任何来自克拉苏军的城外士兵自会像被帕提亚弓箭攻击的时候,很自然地重复地摆出锁盾阵形。没有任何空隙的罗马列队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列队,像一排鱼鳞。力量强大的中国弩箭射穿罗马人的盾牌和盔甲,结果这些人退到城墙后面。②
德效骞还以郅支城的建设来论证罗马军的存在。
罗马人在郅支城的真实存在被中国人发现的城外的双木栅栏(重木城——引者注)③证实。塔恩(Tarn)博士写道:“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④
德效骞认为双木栅栏(doublewoodenpalisade)是罗马人军事防御工事的典型特征,由此推断被中国发现的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证明罗马人的存在,郅支单于在建城池时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同时他论证郅支单于还需要罗马人的军事援助。郅支自然需要得到罗马人的雇佣兵。开始时他在康居国王的邀请下来到康居,然而成功驱除可怕的乌孙使他与康居国王决裂,为自己建设一座都城。他的名声让大宛(Ferghana)和其他政权向他进贡,以至于他有钱来雇用雇佣兵。另一方面,他没有大量的匈奴人,以至于他被迫依靠附近地区的人的支持。匈奴人住在现在的蒙古,由郅支的弟弟控制,他将郅支驱逐出来,以致郅支不能从那里得到增援。当他在几个康居贵族和几千驮畜的护送下带军前往康居时,郅支遭遇一场严寒,结果整个队伍中只有三千人完成这次旅程。这样他被迫依靠当地人的帮助。当他与康居国王决裂及杀害国王的女儿时,他冒犯许多康居人,因此自然地会向外寻找雇佣兵。罗马人在他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条件下,被这位著名的武士吸引,结果是相互吸引。①
德效骞认为郅支单于在与康居国王关系决裂,拥有大宛等政权进贡钱财以及他的部众因严寒而锐减、得不到匈奴其他部落的支持等情况下,他可以利用获得的钱财来雇用军事力量为己服务,而罗马人在郅支单于答应与帕提亚人为敌的前提下,答应为其服务,由此得出罗马士兵与郅支单于出于相互的需要而彼此吸引,最终走在一起。得出此结论后,德效骞又进一步地论证摆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
又一个问题排列成鱼鳞阵的士兵是罗马人还是罗马人训练的当地人?我们在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信息必须靠猜想。当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他用马其顿(Macedonia)的作战方式训练当地的年轻人,结果他从印度回来时,他的总督带给他大约3万这样的年轻人。然而亚历山大有不可抵抗的征服者的声誉,反之克拉苏军团可耻地失败。人们自然不会模仿战败的流亡者的装备和作战方法。希腊国王有时也用希腊风格武装他们的国民,但这些王国是希腊人,有希腊将军。罗马的声誉如果在康居被人知道,一定在这个距离罗马帝国遥远的地方大打折扣。而且成功的龟甲阵需要相当多的技术和拥有罗马人的盾牌,我对除了专业士兵之外的任何人能够应用它表示怀疑。郅支在中国人攻击他之前待在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②
德效赛认为鱼鳞阵需要专业的士兵,技术含量高,而郅支单于来到康居的时间不到5年,于是认为当地人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训练,达到运用鱼鳞阵的水平,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让我们认为这一百多名步兵实际上是罗马军团”。那么在郅支之战中,这些罗马士兵有着怎样的遭遇呢?
当城被攻击、郅支的宫殿被烧毁及其头颅被砍掉的时候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陈汤报告总共1518人被处死(可能大部分是匈奴人),145名敌人被活捉,一千多名敌人投降。这些人被(作为奴隶)分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15个国王,他们是中国的附属国,前来起辅助作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名郅支单于的人逃掉。145名俘虏的古怪数字必定是这些罗马雇佣军的数字。中国人想要康居人保持好的印象,因此追随郅支单于的康居本地人可能被允许逃跑,投降的1000多不是康居和罗马的雇佣军。如果这些罗马人没被杀(雇佣军通常能成功地照顾好自己),他们可能被带到新疆,一些人甚至来到中国。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在郅支之战中活捉的145名俘虏是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而这些罗马士兵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那么为什么在陈汤上奏朝廷的报告中没有提起罗马人呢?
不用奇怪,陈汤和甘延寿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中没有提起任何罗马人,他们的报告成为《汉书》记载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的信息来源。只有他们中的几个人;中国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罗马,可能不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正如威尼斯人不相信马可波罗(MarcoPolo)关于中国的报告。而且陈汤写报告和送画是为了讨好中国朝廷,因为他必须为矫诏出兵远征的行为赎罪。关于一个遥远国家和几个战俘的描述无助于原谅这样的罪过。戴闻达教授已经表示郅支单于城的记录来自在该地所作的画。我们如果没有所作的画不会知道关于这个特殊军事阵形的任何事情。而且这个阵形来自这样一幅权威的画的事实证明我们将一个广泛的推论建立在单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②
德效骞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罗马,所以不可能相信罗马人的存在,于是陈汤和甘延寿的报告没有提起罗马人,而陈汤的写信与送画都是为取悦朝廷,为自己矫诏出兵赎罪,于是运用戴闻达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汉书》中关于郅支之战的记载来自画,同时鱼鳞阵这个特殊的军事阵形也来自画的事实证明其结论建立在“鱼鳞阵”这个短语的基础上的合理性。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德效骞断定公元前54年被帕提亚俘虏并迁移到马尔吉亚那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兵在康居,在公元前36年中国人进攻郅支单于都城时,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罗马人在都城的修筑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然而郅支单于的战败彻底 破坏这些痕迹,而罗马人确实与中国人发生战斗并被先进的中国武器打败①。
综上所述,德效骞在这篇文章中,说明在公元前54年于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首先被帕提亚人安置在马尔吉亚那,然后他们以雇佣兵为生,于是势单力薄的郅支单于雇用了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修筑了郅支城;在郅支之战中出现在汉军面前的“鱼鳞阵”不可能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罗马人,同时这种阵形需要严密的纪律、较高的文明和长期的训练,所以《汉书》中鱼鳞阵的运用者不可能是匈奴人和当地人,而是受雇的罗马士兵;这些罗马士兵在郅支之战中被活捉,可能被带到新疆乃至中国内地。于此,我们可以说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说基本形成。可见德效骞在1940年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提出了罗马军团来华说,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1957年所发表的著作 《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三、德效骞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德效骞在1941年发表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中对罗马军团来华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首先他在文中论述作为古代世界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相遇只能出现在中亚地区。
罗马人和中国人是古代世界两股最伟大的军事力量。在罗马人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an world )的时候,处于汉代(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征服他们的世界里所有值得征服的地方。如果来自这两股力量军队的相遇,可能只会出现在中亚,因为罗马的势力远远没有到达地中海的东边,而中国人几乎没有发现去帕米尔(Pamirs )以西地区的价值。这样的相遇没被注意,因为我们唯一的证据是1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单个奇怪的短语。②
德效骞认为中罗军队只能在中亚相遇的原因在于罗马人在地中海以西活动,而中国人则一般在帕米尔高原以东活动,而中罗军队在中亚的相遇以前未被世人注意,主要在于其证据只是公元1世纪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奇怪短语即“鱼鳞阵”。中罗军队的首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远征康居,进攻匈奴郅支单于的事件。
这次相遇来自公元前36年中国西部前沿地区(新疆)的都护做的一个事实,在他自己的职责下,一次到康居(Sogdiana )的远征取走匈奴 (Hun)郅支单于的头颅。匈奴人占领现在的蒙古(Mongolia )。匈奴王位(匈奴皇帝被称为单于)的一个竞争者,他的部落名是Luan-ti,名字是呼屠吾斯(Hu-t'u-wu-szu),统治头衔是郅支骨都侯(Chih-chihku-tu-hou),因此他一般称为郅支单于,杀死一名中国使臣,逃入西方,他被康居国王邀请前往那里,赶走入侵的游牧民族。在显耀功绩的助长下,郅支单于梦想在中亚建立一个帝国,在都赖水(怛逻斯河,Talas)边建立自己的都城,从周边部落获得贡品,一些部落也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中国的副都护陈汤看到这股新力量对中国利益的潜在危险。他集合驻扎在中国西域的军队,在当地政权的辅助下,说服他的上司随征,并出发。
军队成功地走了1000里的长途行程抵达郅支都城,在这里他们立即攻击并占领该城。这次杰出功绩的记载,最近由戴闻达博士数次提及。他表示中国人的西汉历史,我们的唯一原始资料,其信息大量来自一些被陈汤呈送给帝国朝廷的战争画。在此记录中有不同一般的评论,在攻击开始时,郅支城外有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在门的两侧。这个奇怪评论的事实来自一幅画的描述,这给它以不同寻常的可靠性。①
郅支单于在杀害汉朝使臣后,受康居国王邀请,来到康居赶走入侵康居的少数民族,在都赖水旁建立都城,其势力在中亚逐渐兴起。陈汤看到郅支单于的威胁,便集结军队远征,攻击郅支单于并占领该都城。德效骞运用戴闻达关于《汉书》对此次事件的记载来自陈汤呈送给朝廷的画的研究成果,认为100多名步兵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事实由于来自一幅画的描述,因而是可靠的。那么鱼鳞阵来自何处?
鱼鳞阵不是一种简单完成的策略。这些士兵必须挤在一起重叠他们的盾牌。这种策略需要整个群体的一致行动,特别是面对攻击的时候,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发现只有在一支专业军队中应用。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士兵据记载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以混乱的人群冲入战场。
马其顿步兵盾牌圆而小(直径只有1.5英尺),所以无法重叠它们,反之罗马军团拿着大的长方形盾牌,容易连在一起,组成一个保护层抵挡飞弹。然后我们必须寻找某种罗马人能在队列前形成类似鱼鳞的战术以及寻找位于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②
鱼鳞阵是一种复杂的阵形,需要集体的一致行动和高度的纪律性,只能在专业军队中运用,德效骞认为当时有规则阵形的专业军队只能是罗马和希腊,于是对希腊和罗马人的盾牌进行了比较,得出:因希腊人的盾牌圆而小,无法摆出鱼鳞阵;而罗马人的盾牌是长方形,容易拼在一起形成鱼鳞状的保护层。于是他认为鱼鳞阵来自罗马而非希腊。那么出现在中亚腹地的鱼鳞阵是罗马人提供的吗?于是他开始在中亚腹地寻找罗马军团的踪影,而在当时能够出现在中亚腹地的罗马军团可能只有在公元前54年卡莱战役中战败被俘的克拉苏旧部。于是他对卡莱战役进行描述。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带领7个军团进军帕提亚,其中4000骑兵以及同等数量的轻装士兵。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包围罗马人,整天不断发射致命的箭。罗马军团无用,因为帕提亚骑兵在他们冲锋之前撤退,结果罗马人不能抓住他们的对手。在克拉苏儿子普布利乌斯(Publius)指挥下的辅助骑兵和一些军团发动的一次决定性的冲锋,使这股力量与主力分开。为了防御帕提亚的箭,军团只能组成一个方形,环绕以锁盾。
最著名的罗马阵形是龟甲阵(testudo),在此阵中盾牌锁在一起,在城墙下开展军事行动时,用锁在一起的盾牌放在士兵头上以保护他们。似乎没有记载在这种阵形中罗马士兵也在边上锁盾。在图拉真(Trajan,98—117)纪念碑中发现的龟甲阵样式,罗马军团不仅头上有锁盾而且他们的左边也有。前进时可能难以在右边和前面锁盾,但是当站着不动时,易于形成方形锁盾。然后克拉苏军团的锁盾行动是龟甲阵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把锁盾放在头上,因为普鲁塔克(Plutarch)的原始材料陈述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的人在与主力被切断时,退到一座沙丘并锁盾,但那些人在高于沙丘处,从高于盾牌处发射,因此他们被帕提亚人射中。18年后,安东尼(Antony)的人改进他们的战术,当同样遭到帕提亚骑兵射手攻击时,前排屈膝,将盾牌放在地上,保护后面人的脚,第二排将他们的盾牌举到头的位置,其余人将盾牌举在头上,这样完成龟甲阵。用这种方法,整个军队免受帕提亚的箭,安东尼的人安全撤出。然而,克拉苏的人只是组成单边的锁盾,帕提亚人以高过外面士兵的头的轨道射箭,在自己免受危险的情况下消耗罗马的力量。
在锁盾以抵挡箭方面,希腊人和几乎其他每个人用的圆形或椭圆形盾牌是无用的,只有罗马人的长形盾是有效的,长形盾在外形上是长方形 (形状上为半圆柱形)。一排罗马长形盾在沿着前排步兵延伸得没有间隙,对于之前从未见过此种排列的人而言,看上去像鱼鳞阵,特别是因为它们的圆形表面。否则确实难以描述。
卡莱战役对罗马人是严重的灾难。在随克拉苏出发的42000人中,几乎不到1/4的人逃出。2万人被杀和1万人被俘。帕提亚人押送这些罗马囚犯去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处中亚包括现在的木鹿)去守卫他们的东部前线。1万人中有多少人到达该地,我们不知道,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大约1500里,俘虏在这样的征途中难以得到善待。罗马和希腊记载实际上没有关于这些人的进一步报道。贺拉斯(Horace)猜想这些罗马人与野蛮的女人结婚,在帕提亚的军队中服务。①
帕提亚的军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利用罗马军团龟甲阵的弱点,用弓箭射杀罗马士兵,并最终在卡莱战役中获胜。他们将被俘的1万名罗马囚犯押往马尔吉亚那,为其守卫东部边界。那么这些罗马战俘是怎么和郅支单于产生关系的呢?
帕提亚边界、阿姆河边的马尔吉亚那到都赖水边的郅支单于都城大约500里,从克拉苏战败到中国人看见人在郅支城前排成鱼鳞阵时隔18年。这些罗马军团习惯于以专业士兵谋生,希望成为雇佣兵。当郅支单于在康居国王邀请下来到康居时,由康居贵族和几千驼畜护送,骑兵遇到严寒灾害,以致全部人马只有3000人度过旅程。后来郅支单于因军事成功而自满,与康居国王决裂,杀死自己的一个妻子、国王的女儿,修建自己的都城。他不能希望从匈奴获得支持——他们归于正统的单于统治,该单于是他的敌人和半个兄弟,得到中国人的支持。郅支单于由于其专横的行为也与许多康居人敌对。因此他自然会从匈奴和康居疆域之外寻找雇佣军。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白刃战战士,他们因他答应成为痛恨的帕提亚人为敌而受到著名武士的吸引。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域经郅支都城到马尔吉安那的安提阿,所以郅支崛起和他需要军队的消息自然传到罗马流亡者之中。②
德效骞认为在马尔吉亚那的罗马战俘习惯了职业兵的生活,希望成为雇佣军,而郅支单于也需要得到雇佣军的支持,因为郅支单于受康居国王之邀来康居的途中,遭遇严寒灾害而势力大减,后来又因居功自傲而与康居国王关系破裂,同时因争王位而得不到匈奴的支持。势单力孤、处境艰难的郅支单于需要雇佣军,而罗马士兵想以雇佣兵为生,于是相互吸引,在得到郅支单于关于与帕提亚人为敌的承诺后,他们成为位于康居的郅支单于雇佣军。德效骞认为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士兵是成为郅支单于雇佣军的克拉苏罗马军团。
在蒙古的匈奴人和帕提亚人一样,战斗时是骑兵射手,然而中国人改进弓,使用弩。一些中国古代的弩如此结实以致要拉开它们需要一个强壮的人背着地,用脚推弓,用手拉弦,这样使用他的脚、背和手臂肌肉的力量。为了控制这些弩,中国人发明不同寻常有效的扳机装置。这些弩是精密的武器,射程比任何其他军队的任何自动武器都远。它们无疑能穿透任何盾牌和盔甲。在进攻郅支城时,中国人自然开始时用一阵弩箭攻击,而他们自己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
以这种方法,中国人甚至射伤郅支单于自己的鼻子,当时他在城内的塔上向进攻者射击。100多名步兵,以鱼鳞阵排列被中国艺术家在郅支城外画出,几乎肯定是克拉苏军团的一些人,他们是郅支单于的雇佣军。被中国弩箭进攻时,他们自然重复克拉苏军队在卡莱的战术。除了拿着长形盾的罗马军团,其他士兵和武器无法产生鱼鳞阵的效果。①
德效骞认为中国的弩很厉害,能够处于匈奴弓箭射程之外,射箭伤敌,在中国军队发射弩箭时,罗马雇佣军重复卡莱战役的战术,摆成鱼鳞阵形。除了鱼鳞阵外,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罗马士兵的存在。
罗马人在此地的存在由双木栅栏得到确认,中国人发现城外有双木栅栏。塔恩博士(W.W.Tarn)说:“我不记得曾在文学或考古学上遇到任何希腊城的城外有栅栏。一个城墙和外面有一条壕沟(一个大的堡垒甚至有三条壕沟)的规则似乎是绝对的。” 然后罗马人一般使用栅栏来加强他们的壕沟,特别是在城门之前。在水上有桥的地方,有栅栏建在两岸的桥上和桥下。被中国人在攻城时烧毁的双木栅栏可能保护郅支城外壕沟上的桥。双木栅栏是罗马人防御工事的标准特征,因此郅支似乎在建设他的城市时使用罗马人的工程援助。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只在北部的蒙古由中国人的叛徒修建少数城镇,在康居郅支单于自然想要他所能发现的最好的军事工程援助,罗马军团能在筑城上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②
德效骞认为郅支城外的双木栅栏可以证明罗马士兵的存在,并且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自身无法修筑城池,郅支城的修建得到罗马军团的帮助。
这些罗马人发生了什么?中国记载陈述当攻城时这些步兵退到城墙后。无疑他们发现中国的弩箭比在卡莱的帕提亚弓箭更有破坏性。中国记录说对于他们没有专门的更多东西。中国人的弩能从城墙上驱赶防御者,结果中国人毫不费力地横扫该城。他们烧毁郅支单于的官殿,取了他的人头,恢复死亡的中国使臣的信用。陈汤报告他处决1518人,这些人可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希望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远征的安全返回。他陈述,另外有145名敌人生俘,1000多人投降。这些人(作为奴隶)被分给西域15个政权的国王,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辅助参加远征。
145名生俘的古怪数字与列队在城外的罗马人的数字(100多)相符合。认为他们与罗马人一致有吸引力。雇佣军通常能在紧急情况下照顾好自己。因此我们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可能仍向东走,去新疆的一些政权。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进一步消息,虽然如果有人去中国很有趣,但是这样的事件似乎几乎不可能。①
郅支单于的罗马雇佣军在战役中受中国弩箭的强有力攻击而不得不败退,德效骞认为他们被生俘,因为《汉书》中记载的生俘的数字(145)与在城外摆鱼鳞阵的罗马士兵数字(100多)相符合,并且推断这些罗马军团继续往东走,被作为奴隶,分给了新疆的一些政权,同时认为这些人去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
最后他总结全文,认为中国人在郅支单于的都城遇见克拉苏的罗马军团,而这些罗马士兵从帕提亚人的手中逃出,并在郅支单于的帐下当雇佣军,帮助郅支单于修筑都城;在郅支之战中,罗马军团因其人数少和中国武器先进而被俘,并被带到新疆②。
将这篇文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古》))与前文 (《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一次军事接触》,简称《公》文)作比较,它们的内容大致一致,但又有一些区别。《公》文明显比《古》文要长,绝不是《古》文的简要版,而《古》文对《公》文在某些方面有所补充。比如补充郅支单于邀请罗马军团兵筑城的原因③,再如补充中国对俘虏的处置,德效骞认为处决1518人可能都是匈奴人,因为陈汤想保持与康居人的友好关系以确保安全地凯旋;145名生虏(罗马人)和1000多名降虏被分给帮助中国人远征的西域15个王做奴隶,因此推断这些罗马军团兵进一步向东方迁徙,被送到中国新疆的某个政权。但《古》文基本否定《公》文中关于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④。在结语中,不同于《公》文,德效骞提出即使在公元前1世纪,欧亚大陆间的旅行存在巨大可能性,民族间的影响也难以限制①。
四、德效骞的《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
1943年,德效骞在学术刊物《古典语言学》(ClassicalPhilology)上发表《罗马人对中国油画的影响》一文,主要是为前面两篇文章提出佐证,证明罗马与中国之间在公元前36年发生过一次军事接触,证明《汉书》中所记载的145名生虏是克拉苏罗马军团兵。他在该文中首先对之前的观点予以梳理。
前段时间我提供了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很有可能俘获100多个克拉苏军团士兵的证据。这些人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人俘获的成千上万人之一部分,并且被运送至马尔吉亚那。他们逃跑并且向东朝着中国沿着丝绸之路行走了500英里,来到正由匈奴单于郅支建设的城镇上,他们为其提供援助。一群由中国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助手陈汤领导的中国远征队,侵袭和俘获这个城镇。就目前的讲述,我将提供有关这些罗马人之后历史的证据。②
这段叙述是对德效骞前面两篇文章的总结,简要地讲述了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俘的克拉苏罗马军团士兵经过被帕提亚人运到马尔吉亚那,由此逃跑来到郅支单于的都城,并参与此城的建设,在汉军占领该城的战役中再次被俘的经过。至于其被俘之后的情况,德效骞在文中作进一步阐述。
德效骞采用戴闻达的观点,认为陈汤关于郅支之战的报告应包括一系列画,并提出这些画不同于之前的中国画。
这支远征队在许多方面很特别。陈汤关于他的战役的报告包括一系列画描述了对单于城的攻击和俘获——这在之前的中国艺术中是不为人知的。荷兰莱顿大学(LeidenUniversity)的戴闻达(Duyvendak)教授陈述说这些图画包括具有最早记录历史事件的中国绘画作品,其特点复杂,似乎有各种元素得到逐一分析,并形成了一幅混合图画。我相信这在中国艺术中是新出现的。
之前中国画利用的主题是神话、传说以及教化的奇闻逸事。这些是中国画和素描中仅保留和传下来的主题和描述。陈汤的画似乎是中国第一批描绘当代事件的绘画作品。对于朝廷来说,这些作品具有不同寻常之处,因为这些作品展示在每年的新年朝廷宴会上,甚至对于后宫的宫女们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图画。在那次远征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主题,这似乎对中国艺术来说是新东西,刺激这种变化的缘由是什么?①
德效骞认为陈汤的画反映的是当代事件即攻击和俘获郅支单于的经过,与之前的中国画不一样,因为之前中国画的主题是神话、传说及有教化功能的奇闻逸事,同时陈汤的画还有不同寻常之处,即其在新年朝廷宴会上展示,并吸引了后宫的宫女。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在那次远征中,陈汤取得重大胜利且没有给帝国财政增加任何格外支出,比以前更进一步地将中国军队向西成功地推进,即便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还是为一个中国使者报仇,杀死闻名整个亚洲北部的匈奴武士。为了组织他的远征,他伪造了朝廷诏书,这不仅是死罪,而且拘泥于形式、信奉儒家的大臣对他也有偏见。而且他的上司——都护因拒绝迎娶宦官的姐姐而致命地冒犯了掌权的、控制政府的宦官。因此中央政府最具权力的影响人物都反对陈汤。他明白,除非他以非常生动的方式吸引朝廷对其成功的注意,否则他和甘延寿将受到惩罚。
而且陈汤不是一个自满和骄傲的中国人。他对外国的情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很想向他们学习,具有高超的想象力。他特别善于接受并且非常渴望听到任何新事物。
在这次漫长的返程中或之前,陈汤成功地召集罗马军队的领导,并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说自己的祖国。他们之前的功绩表明他们的领导必然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当时情形下(一个取胜的将军回家),很自然地将罗马凯旋行进的情况(凯旋)告诉陈汤。克拉苏的军队有部分是庞培 (Pompey)的老兵,因此这些罗马人可能目睹或参加公元前60年庞培的伟大凯旋,这仅发生在卡莱战役7年前。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场,他们也肯定从他们的同伴中听说过这一切。
使用画来表现罗马人的凯旋是众所周知的。“孔沿塔代表着被俘的城市,图画和雕塑展现战争的功绩。”在庞培的凯旋中,有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以及与他一同死去的女儿们,以及早于他死去的儿女们的图画。维斯帕先 (Vespasian)与提图斯(Titus)的凯旋中,“战争在各自的部分中由许多手法展现,提供一幅由有趣的事件构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②
德效骞首先从陈汤的处境出发来进行分析,认为陈汤虽然获得巨大胜利,但是其处境异常困难,因为矫诏出征和婚姻问题引起朝中权贵——大臣和宦官的反对,于是,陈汤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处境,必须强调自己的胜利。那么,以何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呢?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高度想象力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采取罗马军团士兵提供的信息,即使用画来表现凯旋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胜利。将陈汤的画与凯旋联系起来,这是德效骞听从哥伦比亚大学MosesHadas教授的建议的结果①。德效骞认为《汉书》对郅支之战的描述实际上是九个场景也即九幅画。下面将德效骞所描绘的九个场景与《汉书》中的文字相对照。
德效骞的描述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有少量出入,比如缺少单于在听到汉军前来的消息后,由出逃转为坚守的决策变化过程。《汉书》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①还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德效骞将《汉书》中的“重木城”翻译为“doublewooden palisade”,意思为“双木栅栏”。德效骞认为这九个来自《汉书》的场景与约瑟夫的代表作很相似,是《汉书》中唯一一次对战争的生动记录,而且中国人没有类似凯旋的活动,因而推断班固撰写《汉书》时参考了陈汤的画,陈汤画的灵感来自罗马人的凯旋。这些来自中国历史的场景与约瑟夫(Josephus)对罗马人凯旋的描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这是《汉书》中能找到的唯一一次关于战争的生动记录。班固独自编写他的历史,几乎完全来自朝廷图书馆的文件资源以及档案,可以获得关于战争的书面报告以及图画。中国人除了在胜利军队归来之时设宴庆祝的习俗,没有类似凯旋的实践活动。陈汤这样具有想象力
① 《汉书》,第9册,卷七十,第3014页。
和敏锐眼光的人,在听到罗马人的凯旋以及再现胜仗的各个场景的描述后,他很可能抓住这个特征,将之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元素,生动地描述其不同寻常的胜利以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汤送入中国朝廷的画是如此富有感情,必定来自凯旋中罗马人活动的灵感。如果这个推断被接受了,我们则可以猜测这个画家。从这些场景的特征来看,罗马人可能对这些画的主题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士兵们出现在画中,并非以不合适的方式。中国军队远征随身带着画家和制图者以保留地理和路线记录。然而,罗马指挥官可能选择当地他所熟悉的画家以准备这些场景。佛教信徒的画很可能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或许是在罗马人或陈汤或者其他中国人的建议下,由一位当地的康居人和一个中国人合作完成。①
德效骞认为虽然这些画的主题来自罗马人的指导,但是画的作者不是他们,因为罗马凯旋主要通过舞台造型或人物雕塑来表现,绘画只用于次要的场景,所以推断画的作者是中国人和康居人,他们对罗马人的做法进行了改造,改变了凯旋的表现方式②。
按照上述推理,在郅支之战中被汉军俘获的罗马士兵对陈汤讲述了罗马人庆祝胜利的方式——凯旋以及对陈汤的画造成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陈汤提供了帮助,那么陈汤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那么现在我们对罗马人的最后处置应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陈汤从罗马人获得如此有价值的援助,那么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中国历史对这145个(罗马)步兵毫无记载,仅仅说到这些俘虏被作为战利品(奴隶)分给附属政权的国王,这些国王参加了中国人的远征。而且陈汤的官方报告未提到他的收获,从其他地方,我们得知陈汤觊觎这些战利品,违背法律,在他进入中国之前,拿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该期待我们唯一的来源——历史,提到这些(罗马)俘虏,因为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而中国历史很少有关于奴隶的记载。③
德效骞认为陈汤为了报答罗马士兵所提供的帮助,很可能将他们带到中国本土。虽然《汉书》的记载提到这些俘虏作为战利品被分配给西域的政权,但是德效骞认为中国历史对奴隶不重要,所以关于这些俘虏的下落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史书,因为他认为这些罗马士兵被安置在骊靬县。
然而,我们可以很肯定地陈述这些罗马人的居住地。公元5年,朝廷地籍上列出一个名叫骊靬的城镇。这个名字与中国人用于称呼古代罗马世界的名字一样。在公元9年,中国的王位被王莽篡夺,他开始建立上帝之国,其中所有的名字都与现实相对应。他将骊靬更名为揭虏,两个汉字意味着“抚养贱民(囚犯)”和“攻下城市获得的囚犯(俘虏)”。
中国本土使用外国的地名,在汉朝,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意思——这个中国地方居住着来自国外的居民。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有两个这样命名的例子:现在陕西北部的一座城市与库车的名字相同,在陕西南部一条山脉叫做温宿。库车和温宿都位于新疆。关于这两个中国聚居地,我们特别被告知来自那些外地的居民被安置在这些中国聚居地。然后来自罗马帝国的人们几乎断定在公元5年之前就已经移民到中国,且居住在骊靬。而且,王莽的新名字说明他们是俘虏。①
德效骞认为骊靬是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而汉朝出现了以此为地名的一个城镇,这个地名在王莽建立政权后,为了表示与现实相对应,改名为“揭虏”,强烈地表示着该地的居民为囚犯(俘虏)。同时他以库车和温宿为例来说明汉朝有将外来居民安置在中国,并以该国国名命名定居地的传统。于是骊靬县的出现、骊靬为中国人对古代罗马的称呼、王莽将骊靬改名为揭虏的事实以及汉朝以外国国名命名外国移民定居地的传统,成为罗马士兵移民到中国,并定居在骊靬的有力证据。这是德效骞第一次提出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骊靬的观点,此时为1943年。同时他还指出了骊靬县的方位。
古代中国骊靬位于现在永昌南部,永昌城位于甘肃省西面的一条峡谷。该地在公元前121年由中国人从匈奴人手中占领,在那个年代,其居民已经迁移至一个遥远的地方。因此该地逐渐由中国人居住。公元前79年,匈奴侵略该地区,包括骊靬附近的番和。由于骊靬在这个时代没有被提及,或许这个地方还不存在。在公元前35年,当陈汤从康居返回,这个地方很可能有部分无人居住的地区,政府想在此地区殖民,以守卫丝绸之路。到公元5年,该地区有被来自罗马领土的俘虏居住。班固详细记录了中国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除了跟随陈汤的队伍外,没有任何情况能让这么多罗马俘虏进入中国。②
骊靬县位于今永昌县南部,他认为陈汤从康居回来时,该地有部分无人居住区,政府想在此殖民,目的是守卫丝绸之路,于是公元5年被汉朝俘虏的罗马军团士兵被安置在此,这也是班固在详细记录公元前1世纪中国历史时没有提及罗马俘虏进入中国的原因所在。
德效骞在文章末尾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帕提亚人有效地阻止了罗马通往中国之路。任何罗马人能穿越他们的领土的唯一途径是作为战争囚犯的俘虏。位于帕提亚和中国之间的部落只允许小群的商人通过,而阻止任何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的军队护送。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从罗马移民进入中国,唯一能克服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中国西部骊靬的存在很好地证明陈汤确实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以及他把他们带入中国,并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古代中国称呼罗马世界为骊靬的地方。而且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的内容,并且开创后来以画的形式记录战役的惯例,这个惯例起源于罗马的凯旋。①
德效骞认为罗马人进入中国要经过两者之间的帕提亚以及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而帕提亚人不允许罗马人穿越他们的领土,除非作为战俘,同时帕提亚与中国之间的部落政权也不允许大量的移民进入,除非有强大军队的保护,唯一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是公元前53年帕提亚俘虏的克拉苏军团以及公元前36年冬至前35年期间陈汤的中国远征军。他认为骊靬在中国西部的存在能够说明陈汤与罗马军团在康居东部相遇并将后者带入中国,安置在骊靬县,而这些罗马人影响了中国画,开创了中国画记录战役的传统。
五、德效骞的《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
德效骞于1957年在《希腊与罗马》(GreeceandRome)杂志上发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ARomanCityinAncientChina”)。这篇文章对其以往关于罗马士兵来中国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德效骞首先依据公元5年出现骊靬地名,肯定地提出罗马人一定移民来到中国,并建立骊靬这个城市。他指出骊靬城在今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
在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和县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用非常古老的中国对罗马称呼来命名的城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他们的城市起外国的名字。在那个清单上,有1500多个城市,只有其他两个城市使用外国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居住着来自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得出罗马帝国的人一定移民到了中国,并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结论。
这座用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命名的城市位于现在的永昌南部,位于甘肃省狭长的西北部。在公元前79年不存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是公元5年登记中国城市的时候。也有名字由篡权者王莽命名,他用儒家思想来纠正名字,也就是说对任何东西都给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座城市他重新命名为揭虏,这个词语包含两层意思:“在占领一个地方时候拿下的胆小鬼【被俘虏】以及‘抚养的胆小鬼’。”然后,是不是中国人抓到一些罗马军团的囚犯,然后将其安置在中国西部边界以保卫边疆?①
德效骞认为公元前79年不存在骊靬城,到公元5年出现,这座城池后被王莽改名为揭虏,于是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抓到罗马军团的囚犯,将其安置在此以保卫边疆?
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有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对罗马充满仇恨,不允许罗马人大量过境,那么这些到中国境内建立骊靬城的罗马人是如何穿越帕提亚帝国的呢?德效骞提出疑问后,开始回到罗马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之中”,并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将欧陆两端联系在一起。他首先从罗马三巨头庞培、恺撒、克拉苏之间的关系讲起,认为克拉苏在三巨头中的优势是经济,而不足确是罗马人最为看重的军事。
公元前60年,在罗马,罗马元老院将凯旋授予庞培(Pompey)将军。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到罗马,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助。恺撒 (Caesar)和克拉苏(Crassus)来帮助他,并形成了第一次三人执政。恺撒在59年成为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在55年也成为执政官。后者后来成了叙利亚总督。
克拉苏对三人执政贡献了大笔资金,这是其他两个人所缺乏的,但是他们的计划所急需的。同时他最缺乏和最想得到的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军事荣耀。他来到叙利亚之后,不顾他最好的将军的建议,向帕提亚人发动战争。公元前54年,他带着42000人进军帕提亚人的领土。帕提亚人在卡莱(Carrhae)与他遭遇。他们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射手组成,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并不断发射一连串致命的箭。骑在马背上的帕提亚人在罗马人上来之前撤退,,越过他们的马匹尾部发射,罗马人陷入无助境地。罗马军团只能形成一个方阵,在四周用锁盾来保护,这样就形成典型的罗马阵形——龟形阵。但是帕提亚人朝罗马人盾牌的上、下方,毫无危险地屠杀了罗马人。到傍晚,20,000人被杀死,10,000人被抓为囚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乘夜逃跑,到达叙利亚。①
克拉苏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出任叙利亚总督后,不听旁人劝告,急切地向帕提亚发动战争。结果,克拉苏打败,罗马军团有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接着德效骞对这些俘虏的下场进行考察。
我们不知道那些囚犯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林尼(Pliny)说他们被迁至马尔吉亚那(Margiana),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这是中亚的一个地区,包括现在的梅尔夫(Merv)。这10000人当中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从卡莱到马尔吉亚那的安提阿(Antioch)的距离超过1500英里,俘虏在这样的行军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好的待遇。我们的信息到此为止。古代诗人贺拉斯(Horace)猜测这些罗马人迎娶了蛮夷妇女并服役于帕提亚军队。②
德效骞运用普林尼的说法,认为罗马战俘被帕提亚安置在马尔吉亚那,以守卫帕提亚的东部前线,由是罗马人从帕提亚西部来到了东部边界,穿越了帕提亚帝国,为其进一步向东迁徙埋下伏笔。
接着,德效骞开始研究中国方面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中国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一个世纪,现在的蒙古被匈奴人占领,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人。他们的皇帝名叫单于。公元前60年,当他们的单于去世的时候,一场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导致8位请求者将自己立为单于。不久所有的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两个:单于呼韩邪(HU HANS工E)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郅支(JZH-JZH)。当郅支在战争中打败了呼韩邪,后者从中国人中寻求援助,并派他的儿子给中国帝王做随从。中国的惯例是将结盟的外国王子控制在中国朝廷,一方面是作为他父亲良好行为的人质,另一方面是向他灌输中国文化和权力。郅支也派他的儿子来到中国朝廷。呼韩邪很礼貌地请求许可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朝廷,并表示其忠诚。他得到隆重的接待。宣帝很明智地把单于作为客人,并封他为与帝王一样的级别,位于中国人的王和其他高官之上。单于被给予丰厚的礼物,两个月后被护送回内蒙古,在那里他被许可占领某些中国边远要塞。中国人支付高昂的费用以防止给匈奴人入侵中国边界。在这几年中,中国人因为呼韩邪的追随,送给他20000蒲式耳的谷物,这样他就能吸引大量的匈奴来跟从自己。
郅支害怕他的对手,离开了蒙古,向西走去,试图与乌孙(WU SUN)联合,乌孙可能是哥萨克人(Cossack)或者吉尔吉斯人(Kirghiz)。然而他们杀死了郅支的大使,并将这个人的人头送到中国。郅支惊人地成功打败了乌孙的军队。但他不能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向北方前进并占领了现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国。1000英里的草原对匈奴来说不是很远,比任何蒙古人以及其他草原骑士都远。
郅支认为在这里他会安全的。他于是向中国朝廷送了一封信,要求归还他那作为人质的儿子。守卫中国宫殿的校尉,谷吉(GUJI )(中国人的姓在前面,如匈牙利一样)负责护送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到达郅支王庭时,匈奴将谷吉和他的随从杀害了。①
他讲述匈奴内部的王位之争,主要讲述呼韩邪与郅支之争。呼韩邪赢得汉朝的支持,处于逆境的郅支被迫离开蒙古,向西迁徙,试图与乌孙联合,但乌孙杀害郅支的使者,并讨好汉朝。在这种情况下,郅支打败乌孙,来到西伯利亚西部。在自认为安全的时候,他要求归还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并杀害汉朝的使者谷吉及其随从,由此与汉朝结仇。为了逃避汉朝的进攻,他又必须向更远的地方迁徙,此时他将迁徙的目的地指向了康居。
因为此时康居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康居(Sogdiana),中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郅支作为一个战士的名声很高,康居国王邀请他住在他的国家东部边界,在那郅支有着比寒冷的北方更肥沃的领土,能够保护康居免受乌孙的攻击。郅支害怕呼韩邪和中国人,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建议,签订了一个条约。康居送了数千骆驼、驴和马。然而在路上,旅行队遭受一场冻灾,只有约3000名匈奴人安全抵达康居。国王对郅支表示欢迎并尊敬地招待,与他结盟,将他的女人送给他做妻子。郅支也将他的女儿送给康居国王。郅支现在深入乌孙国内,杀害乌孙人和让乌孙人成为奴隶,赶走他们的牛羊。乌孙不得不撤退,让他们西部的300英里国土无人居住。
于是郅支变得骄傲,破坏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国王的女儿和几百名康居人。他为自己在都赖水(Du-lai river)边建造一座有防御工事的都城。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塔拉斯河(River Talass),它的一条支流消失在锡尔河(Jaxartes)与巴尔喀什湖(LakeBalkash)之间的沙漠中。但是丝绸之路经过塔拉斯河,中国知道这座新城。中国本部西部有一位冠以西域都护头衔的官员,他有一支受过高度训练的自动化中国军队。当都护受中国皇帝命令出征时,在那个区域的小王国派遣军队予以帮助。①
康居因为多次遭受乌孙的侵略,为了自保邀请郅支到康居的东部边界居住。郅支因害怕呼韩邪与汉朝的进攻而接受了邀请。在前往途中,因为冻灾,郅支单于所部遭受巨大伤亡,只有3000人到达康居。康居国王与郅支单于结盟,并互相联姻。郅支单于帮助康居击败乌孙,但因胜而骄,破坏了与康居国王的关系,杀害了康居国王的女儿及数百名康居人。为了自卫,他修建了都城。郅支单于势力在康居崛起的消息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地传播到西域都护的耳中。而此时的西域都护为甘延寿,副都护为陈汤。德效骞认为陈汤“有进取心,勇敢,有计谋,但是不细心”。在郅支单于势力发展的形势下,陈汤认为这很危险,必须消灭这股势力。他看到郅支单于在中亚发展一个大国的危险。他知道在本地辅助力量的帮助下,都护掌握的中国军队能够打败郅支。如果他们等到匈奴获得安全保障,那将会太迟了。他的上级甘延寿赞同,但必须首先获得中央政府同意远征的命令。然而陈汤指出这样一个请求会带来官方的耽搁,过于节俭的帝国朝廷将认为这样的远征太过昂贵。这时甘延寿病倒。
这对陈汤的诱惑很大。他大胆地伪造一个帝国的命令,要求臣属的政权派遣辅助力量,命令屯田的中国军队前来都护所在地开始远征。当甘延寿的健康好转,他了解到部下的行为,他感到吃惊,要求停止行动。但是事实上危险的行为即假造帝国命令的主要罪行已经犯了,不能够停止。因此在威胁和争论之下,陈汤说服他的上级来接受不灭的荣耀的机会。当一支40000人的力量集结,甘延寿和陈汤派人向东到朝廷送一个文件,谴责自己伪造帝国命令、集结帝国军队的罪过。在同一天,公元前36年的秋天,他们向西出发,前往撤回命令无法抵达的地方。②
西域都护甘延寿病倒的情况下,作为副手的陈汤矫诏出兵远征郅支,结果得到甘延寿的支持。在公元36年,他们分兵两路,穿越乌孙,来到康居,寻求敌视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的支持,并从那获悉郅支单于的情况。
接下来,德效骞开始描述郅支之战的情形。他仍坚持认为《汉书》关于郅支之战的描述来自画,但是将之前认为的九个场景变为了八个,这主要是因为他将之前的第四个场景取消了。德效骞以鱼鳞阵、重木城、图画来证明罗马军团在郅支战役中的存在。认为“‘鱼鳞阵’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如此好的鱼鳞阵势的排列需要高度水平的训练和纪律。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或任何未开化的民族一定完成不了”,在排除希腊人后,提出鱼鳞阵就是罗马的龟甲阵,摆鱼鳞阵的士兵就是在卡莱战役中失败的罗马军团;重木城是郅支单于得到罗马人帮助的证据;陈汤报告中的图书说明了罗马人的影响。
他提出史书记载的145名生虏就是摆鱼鳞阵的一百多人,也就是罗马士兵,而且这些人没有投降,只是停止战斗,后跟随陈汤来华,被安置在骊靬县:“当我们将活着的145人的数字与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100多的人数相比,我们几乎不犯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些145名罗马军团没有投降,但只是在他们的雇主被杀后停止战斗。他们可能保持阵形,一个令人生畏的战斗人群。他们实际上自由地选择跟随中国人。在中国罗马人相应地安置在一座专门建造的前线城市,对此中国人当然以他们对罗马的称呼——骊靬(Li-jien)命名。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县城名单中,从王莽的命名中暗示居住在此的人是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获得,被抚养,这一切足以证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①这段记述显然将来华罗马军团的处境大大改善了,由之前所述的“战俘”变成了“自由人”。
1957年发表的《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一文综合以上3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但对以前的观点有所补充和修改。该文补充145名生虏被俘时的状态,认为这些罗马军团兵并没有投降,但当他们见到雇主被杀,即停止战斗,很可能仍然保持难以对付的队列阵势。该文修改《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关于罗马战俘去向的观点,肯定罗马战俘去中国内地的可能性,认为他们甚至自由地选择与中国人一起走,在中国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德效骞认为骊靬的郡县名称,以及王莽的命名(将骊靬改名为“揭虏”,暗指该城由攻城战中的俘虏及其后代居住),都足以说明罗马人确实来到中国②。
在文章末尾,德效骞得出结论: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百余克拉苏罗马军团兵相遇,并将他们带回中国。中国人使用在任何中国文献中均未发现的词语来描述那次远征中的军事布阵,这种布阵只与罗马军队专用的龟甲阵一致。中国人围攻的匈奴城周围有重木栅栏防御,这种防御方式不为中国人或希腊人所用,却常被罗马人应用。罗马人在取胜后常用图画描述战争中的场景,而在中国却从未有过,但这类图画却成为此次中国人远征报告中的组成部分。更为明显的是在公元前79年至公元5年之间,中国建立一座以中国对罗马的称呼——骊靬命名的城市,这个名称表示该城居民来自罗马帝国。①此外,7世纪时,骊靬人发汉语拼音中没有的“x 音,这也说明罗马的影响②。
1957年出版的单行本著作《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与其论文版基本一致,只是比论文版更为详细,比如详细地解释罗马人自愿选择去中国的原因:“他们逃进周边冷酷的沙漠就意味着饿死,因为他们没有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照顾自己的能力。回到帕提亚同样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是从边防卫所逃走的。中国人则欢迎这些勇敢的战士为其戍边。”③在该书中,德效骞还对骊靬城进行构想,认为它“极有可能是按照罗马的模式建造。罗马军团兵并未向中国人投降,是自由人,所以不可能都听从中国人的规矩。按照惯例,只要他们保持和平,纳税服兵役,中国政府通常听其自然。中国人肯定会派一名朝廷命官来管理该城。因为该城存在几个世纪,他们肯定准许与中国妇女结婚。不管是否有某些殖民因素的影响,该地成为一个罗马人的定居点,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罗马人的殖民地。”④此外,该书与论文版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附录中有中英文对照的《按字母次序的汉字》(“Alphabetic ChineseScript”)表。
六、结语
综上所述,德效骞从1940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57年出版著作,可见他对古罗马军团来华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分析他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德效骞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罗马军团的归宿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战俘的生死难以确定,并认为他们如果未被杀害,最大的可能是去新疆,甚至有些去中国内地;《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断定罗马战俘会照顾好自己,不会被杀害,并推断他们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某个国王做奴隶,被带到新疆,而不太可能去中国内地;《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不再考虑他们的死亡问题,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而是在雇主被杀的情况下停止战斗;强调他们不再被当作战利品分给西域诸王,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向,自愿随中国人走,不是去新疆,而是被安置在为他们特设的汉张掖郡骊靬县。可见,罗马军团的待遇是越来越好,他们来中国时是自愿而非被迫,而且来华后受到礼遇,被安置在专门为他们建造的骊靬城。
(二)罗马军团的战斗力问题:《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认为罗马军团兵被中国的先进武器打败①;《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一文则除强调中国武器先进外,还用数量少来解释罗马军团兵的战败②,《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论文版或著作版)则一反前面战败的提法,称罗马军团兵没有投降,他们的战阵让西汉联军难以对付,最终是因为雇主死亡而自动停止战斗③。可见德效骞不仅在不断地抬高罗马军团兵的战斗力,还称赞这些罗马军团兵具有良好的雇佣军职业操守。
当然,德效骞某些观点的调整是因为发现新证据,比如在《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中出现西汉设置骊靬县的新证据。这种自己根据新证据不断调整自己学术观点的行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观点的调整可能存有主观臆断的因素,比如受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西方中心观的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过,永昌虽为西北的一座小县城,但作为古骊靬县的所在地,由于德效骞的研究,以及后来者的推动,进一步成为古罗马军团在华的落脚地,因此而备受世人的关注而扬名于外。
本文是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罗马军团来华问题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骊靬人起源的DNA鉴定
贾笑天
关于骊靬人的起源,国内外的学者,包括生物科技领域的专家都做了大量工作。前不久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组织团队历时两年,对永昌县有特征的人员进行了采血检验。他们用DHPLC法及其他标准方法从87名骊靬男性标本中,将35个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和12个短串行(STR)基因座从人类Y染色体非重组部分中测定出来,15个单体组织得到确认。单体组织的频率分布情况与附近地区的情形相似。在单体出现频率的基础上进行基础组成分析后(PCA)会发现,地理上相近的人们会群居在一起。但是,多维度分析的结果却呈现出一幅特殊的基因图。更出人意料的是,骊靬人与高加索一土耳其一伊朗人关系非常之近。这也就是说,骊靬人从基因上与西亚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情况源于古罗马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西亚地区。这也与有关古罗马人经常雇用西亚士兵的历史记载相一致。对此我和兰州大学陈正义教授就此进行了主题研究,见研究报告《骊靬人的民族构成》。
骊靬人居住在今天中国甘肃省的永昌县。一些人有着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这些体态特征都与其他的中国人相差很远。这些特征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历史、考古学家和记者的关注。他们推测,骊靬人在与公元前53年卡尔莱 (Carrhae)战役后失踪的一支古罗马军团有关联。骊靬人的起源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最近来自甘肃省的一些报道显示,一支古罗马军团在定居甘肃骊靬村落之前,于公元前36年接受匈奴郅支王的统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霍默(Homer Hasenphlugdubs)于1955年第一次提出:公元前53年,在土耳其南部地区的卡尔莱战役之后,帕提亚人俘获了大约10000名罗马士兵,并带着他们向东行进至乌兹别克斯坦,最后加入了郅支部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骊靬人来说,到达中国并不算困难。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一直以来对霍默的假设批评之声不绝,不过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收集大量的历史材料,接受了骊靬人源于罗马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观点。尽管已经做了许多的研究工作,
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霍默的观点。幸运的是,现代分子生物学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人类染色体非重组部分(NRY)相关联的DNA多态保留了我们标本中的父系基因遗传。这也促进了我们对于男性主导的人口迁移历史的研究。将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Y-SNPs)与Y染色体短串行(Y-STRs)结合起来研究,已经证明是研究骊靬人起源的一种强大工具。学者们据此推测出古罗马士兵可能迁移路线。这条路线起始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卡尔莱,然后向东到达中国,最后定居在甘肃省的永昌县。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Y染色体单体分布分析有关骊靬人基因遗传图中获得基因证据时,有关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数据的研究结果可说明,地理上邻近的人口群居在一起的这一情况,这也有可能是Y染色体单核苷多态基因所导致的。大多数已发表的有关,Y染色体变异研究的报告中的观点都有偏颇之嫌,他们赖以研究的系统数据存在失真现象,这有可能是试验人员或者是采集样本过程出现差错所致。
就如在多维度分析中所反映的,骊靬人在基因上与西亚人关系紧密。这一基因上的同质性可以解释为,要么这两种人来自同一起源,要么是两群体间大规模的基因流动,也可能是上述两种现象都有。根据历史记载,大多数罗马军团都是由亚洲雇佣兵组成。所以,骊靬人可能与罗马人没有共同的祖先,而是与西亚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尽管如此,长时间的地理分离也削弱了基因同源的影响。
商业和文化的交往随着基因的流动是符合情理的。自从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西部一直是东亚与西亚人民相会的地方,所以这两个群体间的基因流动也是很自然的事。沿丝绸之路分布的人口也为骊靬人基因库的组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骊靬人在基因上同时也与其他中国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显然,邻近地区群体间的基因流动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骊靬的位置邻近中国其他的民族的聚居区,尤其是中国的汉族聚居区。因此,中国的汉族对骊靬人基因库组成也有一定的贡献。
总之,骊靬人在基因上与西亚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两件发生较早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为西亚与骊靬人之间的联系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一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罗马军团东征及通过丝绸之路的长距离贸易;二是唯利是图的罗马人从西亚向东方移民。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中国人对骊靬人基因构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本文的研究数据取自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
罗马军团、骊靬人民族构成初探
贾笑天 陈正义
一、印欧语系诸民族的形成
(一)印欧语系诸部落的迁移
从西亚、印度到欧洲的广大范围内生活着操印欧语系的各民族。他们是希腊人、意大利人、高卢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伊朗人、印度人等。研究证明,远古时期,印欧语系诸部落繁衍、生息在里海和咸海以北的一片弧形大草原上,该地区位于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广义西域范围内,和现今中国新疆地区相邻。
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印欧共同体开始瓦解,印欧语系诸部落开始向外迁移,其中一支西迁到欧洲,繁衍成希腊人、意大利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一支南迁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成伊朗人和印度人。所以,英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斯拉夫人等西方人其实是从西亚即中国人所说的西域地区西迁形成的。
(二)雅利安人和伊朗人
定居在东方的印度和伊朗的部落又称为雅利安人,该词的意思是“高尚的人” 或“贵族”。雅利安人自认为很高贵。德国人等一些欧洲民族认为自己是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后裔,以至于希特勒在雅利安人的旗帜下发动了世界大战。
伊朗人就是雅利安人的转译。国名“伊朗”的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国家。古代的波斯、帕提亚(安息)就是指伊朗。
公元前2000年中期,印度、伊朗人共同体也开始瓦解。一些部落南迁到了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人,另一些部落则留在伊朗高原,成为伊朗人。公元前1000年初,伊朗部落分布到黑海北部地区、西亚和伊朗高原。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和中亚、伊朗、西亚交往密切。
二、西徐亚人和安息人(帕提亚人)
西徐亚人又称斯基泰人,中国古籍称塞人。西徐亚人是游牧民族,强悍英武,出没于欧亚大陆各地,因此,各国古籍经常提及西徐人。他们曾分布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以东,伊犁河流域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周宣王(前827一前781)进攻猃狁(匈奴),迫使他们向中亚阿姆河流域西迁,从而引发了一场民族大迁徙。西迁到中国的猃狁赶跑了当地的马萨格泰人,马萨格泰人西迁到西徐亚人地区,并迫使后者西迁,引发了其他许多民族的大迁徙。西徐亚人曾分布到欧洲南俄草原等地,他们还在波斯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强盛时曾控制了叙利亚,势力范围曾达到埃及边境。
在咸海地区居住的西徐亚人则和达哈人共同生活,后来同化成帕提亚人(安息人)。西徐亚人以游牧为生,幼年时以骑羊为游戏,长大后成为技艺高超的骑士和英武的战士。西徐亚人和亚历山大大帝作战时,采取了沙漠战战术,围绕包抄,飘忽不定,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使亚历山大十分头痛。后来,帕提亚人(安息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术,被称作“帕提亚战术”。帕提亚弓弩手举世闻名。他们练就了好几种绝招,能给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如他们接近敌人时,先让马慢步走,然后慢跑,最后策马狂奔,当接近敌人时,他们快速向敌人队列放箭,同时快速转向,从马臀上扭身向敌人射箭,此种技艺被称作“帕提亚人的回马箭”。帕提亚人使用“帕提亚战术”和“帕提亚人回马箭”击溃了克拉苏和安东尼等著名将领统率的罗马军团。
三、波斯帝国时期(前550一前330年):东西方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从中国孔子时代到公元前1世纪末的罗马共和国后期(中国西汉后期),欧亚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达到新的较高级的阶段。
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Cyrus前558一前529年在位)和孔子(前554一前479)是同时代的人。公元前549年,居鲁士远征中亚,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大夏,阿富汗北部)、索格狄安那(Sogdiana,即粟特,中国称康居)和花剌子模(Aharezm),控制了中亚乌浒河(阿姆河)和药杀水(锡尔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后来,波斯帝国的领土西达爱琴海、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小亚细亚、利比亚、埃及;东至锡尔河、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北达咸海、高加索山脉和里海;南至印度洋、波斯湾。帝国境内有波斯、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为古代文明和东西方民族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
大流士一世(DariusⅠ前548一前486,前521一前486年在位)登基时帝国境内已有许多希腊人,尤其在小亚西亚部的爱奥尼亚省。他率领主要由亚洲人组成的大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征服了欧洲的色雷斯和马其顿,两次远征
雅典,第一次其舰队在圣山的海域被风暴所毁(前492年),第二次在马拉松惨败(前490年)。大流士一世统一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广大地区,生活着欧亚许多民族,国土从喜马拉雅山脚到爱琴海和北非,面积约520万平方公里,约一千万臣民。他的雕像屹立在由30个臣服民族的代表塑像托着的平台上。
波斯皇帝薛西斯一世(XerxesⅠ约生于前519年,前485一前465年在位)经过四年的精心准备,于公元前481年率50余万士兵,战船一千余艘,大举进攻希腊。西方史学之父,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一前430/420年)感叹道:“任何军队都不能和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薛西斯率领着去攻打希腊呢?”
波斯帝国曾长时期、大规模进攻欧洲的希腊等地。这也是波斯帝国境内各种文化、民族和希腊、罗马文化和民族的一次大交流,给人类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希腊雇佣军,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等亚洲各民族的步骑兵是波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也是帝国版图内各种文明和东西方各民族交流和融合时期。
四、亚历山大大帝:要把希腊文明推向全世界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前356一前323年在世)击杀了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波斯帝国灭亡、亚历山大被尊为大帝。
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基本上和波斯帝国相当,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流域和希腊四大板块。帝国只存在了十余年(前336一前323年),但很有特色,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世界影响极大。亚历山大大帝在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一前332年)的教诲下长大成人,他对自己恩师的爱戴超过了对父亲腓力的感情。亚历山大一心要实现恩师的理想:把希腊文化推向东方,建立世界大帝国,实现欧亚各民族的大融合。
亚历山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远征亚洲,决心建立一个版图超过波斯帝国的“世界帝国”,他东征西战,使帝国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和中亚,南至尼罗河第一瀑布。他曾在埃及征兵,率领马其顿等希腊联军进攻波斯等亚洲地区。
为了实现欧亚民族大融合,他以身作则,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他娶的第一位妻子是巴克特里亚(阿富汗)一位部落首领奥斯亚提斯(Oxyates)之女——罗克珊娜(Roxana)。从民族上讲,罗克珊娜出身索格狄安那(粟特,中国称康居)望族。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又娶了波斯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泰娜(Statira)和另一位波斯公主。在亚历山大的授意下,他手下的80名高官娶了波斯贵族的女儿。上行下效,亚历山大的一万多名官兵也和亚洲女子订了婚。他郑重宣布,马其顿人与亚洲女子结婚,可享受免税权。
在同一个日子,亚历山大和手下的高官及一万多名官兵举行了集体婚礼,演绎了欧亚民族大融合的一段历史佳话。因此,亚历山大的一些继承人波斯化或阿富汗化了,如塞琉古王国的创建者塞琉古一世及其后裔。
亚历山大为建立欧亚大帝国而重用亚洲人。前331一前327年,他统治着十二个行省,其中11个省的总督是波斯人,而只有一个省的总督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卫队也由波斯人组成,这引起了希腊贵族的不满。
亚历山大要征服所有的陆地,要建立“世界帝国”,加之亚历山大的老部下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思乡心切,不愿继续远征,亚历山大乘机对军队实行大换血,招收大量的亚洲人入伍,如出征印度时招募了三万伊朗人,后来又征召了三万巴克特里亚(大夏)青年入伍。亚历山大顺应马其顿人的愿望,让他们退伍回国,吸收了大量的亚洲人入伍,后来,他的军队主要由东方人组成。许多马其顿官兵退伍回乡之际,将亚洲妻子和儿女留在服役地,主要原因是怕带着亚洲妻小回老家会和原来的妻子发生矛盾,这样,希腊人在亚洲留下了自己的后裔。
亚历山大曾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撒马尔罕一带和索格狄安那人大战,杀死了十二万康居(索格狄安那)人,攻占了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后来成为康居国的首都。这次惨重的牺牲,在索格狄安那(康居)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同时,亚历山大欣赏康居人的英武,征召大批康居人人伍。
康居和西汉帝国关系密切。陈汤远征匈奴郅支单于时,曾深入康居境内,并和康居军作战。陈汤在康居境内消灭了郅支,引起康居人恐慌,因此,汉成帝时(前32一前7年),康居使者赶到长安,向汉帝国纳贡称臣。康居人会把亚历山大等西方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反之,也会把中国人的信息传递给西方人。
亚历山大大帝开创了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和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希腊化时代。他在征服的领土上建立了70多座亚历山大城,这些城市按希腊模式修建,每座城市中有希腊移民一万多人,许多商人也集中到这些城市,希腊文化由此传播到四面八方。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在阿富汗高原建成四座希腊化城镇,在药杀水(锡尔河)河畔、粟特(康居)、印度、印度河等地修筑了许多亚历山大城。这些城市居住着希腊移民,是希腊化基地。
亚历山大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市(Khud—zhand,曾称列宁纳巴德)修筑了城市,命名为“最远的亚历山大城”。苦盏市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西汉时属大宛国,距现今中国边境三四百公里,西汉时中国军队、使者、商人不断到达这些地区。
古文献记载,亚历山大在阿姆河河谷留下了13500名士兵驻守,仅在阿拉霍西亚Ara—chosia就驻扎了4600名;亚历山大死后有23000名希腊军人定居在伊朗北部和中亚。亚洲人把亚历山大称作伊斯坎德(Iskande),现阿富汗坎大哈
(Kandahar)由亚历山大修建,坎大哈就是伊斯坎德的转音。
在中亚,亚历山大扩张到锡尔河靠近现在中国边境的地方。有人甚至认为,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可能深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英国权威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推测,若亚历山大再长寿一些,他会征服西方及印度,然后在公元前314年奇袭战国时代的中国。
罗马人和亚洲国家交往密切,他们曾派使者拜访过亚历山大,由以上史实推断,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不少有关东方和中国的消息。
五、塞琉古王国(前312一前64年)和希腊化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但希腊化进程继续发展。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为三个主要国家,其创建者都是亚历山大的得力部将,它们都以建国者的名字得名: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希腊的安提柯王国和亚洲的塞琉古王国。三国中塞琉古最大,版图包括原亚历山大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它西至爱琴海,东到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和后来中国西汉的势力范围相重叠。帕提亚(安息)王国和希腊一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王国也曾属塞琉古王国。
塞琉古王国的创建者是塞琉古(Seleucus,约前358一前280年),称塞琉古一世(前305一前280)。他把国都定在当时叙利亚北部的安条克(Antioch,现土耳其Antakya安塔吉亚)。中国史籍称该王国为条支,可能是其国都安条克的转音。塞琉古是希腊人,其王后是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大贵族斯皮特美尼斯的爱女阿帕姆,所以塞琉古王朝也被称作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朝。塞琉古王国继续推动希腊化进程。原是希腊人的塞琉古一世及其继承者为了巩固政权,积极实施将希腊等欧洲人移居亚洲并与亚洲人共融的计划。他们继承亚历山大的计划,也在境内修筑了几十座希腊城市,按希腊方式实行自治,每个城市相当于一个小共和国,是传播希腊文化和欧亚民族融合的基地。
从塞琉古独立出来的帕提亚王国(安息)也深受希腊化影响。塞琉古王国的东部分离出希腊—巴克特里亚(大夏,即阿富汗北部)王国,统治者是希腊人,疆域达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东西方文化、民族在此交会、融合,对印度、中亚、中国等国家影响极大。张骞所到的大夏就是这样深受希腊化影响的国家,这里生息着相当数量的希腊人等欧洲人及其后裔。汉民族通过大夏应该知道许多有关希腊和罗马等国的信息。
六、罗马和塞琉古王国的战争
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实行扩张政策,获得成功。他和托勒密王国进行战争于前198年夺得巴勒斯坦、科埃莱—叙利亚等地。他乘胜渡海攻入欧
洲,占领了色雷斯等地(色雷斯在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之北,位于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希腊境内)。
他重建著名的莱西马基亚城,并向此大量移民,以便控制色雷斯。他进而和罗马争夺希腊等地。一些希腊城邦向他臣服,但另一些城邦不甘受他的控制,并向罗马求援。罗马也早就想控制希腊。因此,双方兵戎相见。
公元前192年,罗马和塞琉古王国发生战争(又称叙利亚战争),次年,罗马击溃了安条克三世的军队,将塞琉古势力逐出希腊。
公元前189年,在马格尼西亚决战中,西庇阿率领罗马军队,再次大败安条克三世的军队。次年,双方签订和约,安条克放弃了小亚细亚和色雷斯,塞琉古王国从此失去了地中海强国的地位,罗马进入西亚,在小亚细亚建立行省。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国被庞培所灭。
从上述罗马和塞琉古的战争,人们可窥视欧亚民族交流、融合的概况。罗马、塞琉古两国的臣民几乎包括欧亚所有民族,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欧亚民族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七、从米特拉达梯战争看欧亚民族交流
(一)本都和罗马的冲突
本都位于黑海南岸的土耳其西北部地区,是一个希腊化国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为争夺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霸权同罗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史称“米特拉达梯战争”。
米特拉达梯家族传说是波斯阿黑美尼德王室的后裔,具有波斯(伊朗)血统。前121或前120年米特拉达梯之父米特拉达梯五世在宫廷阴谋中丧命,年仅11岁的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idateⅥ前132或前131年出生,前121/120—前63年在位)继位,由其母拉奥季卡摄政,但她专横跋扈,竟想谋杀亲生儿子。米特拉达梯六世被迫隐匿山林,历尽艰险。公元前115年,米特拉达梯复位,残酷报复,将其母杀害。
米特拉达梯崇拜亚历山大大帝,梦想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他继承其父的扩张政策,吞并了东邻小亚美尼亚、黑海东岸的科尔基斯(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境内)。此时,黑海北岸的希腊人受到斯基泰人的威胁,向本都求援。米特拉达梯出兵克里木(现属乌克兰),击溃斯基泰人,使黑海北岸希腊化城市和博斯波鲁斯王国(现黑海东北岸和亚速海东岸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带)归顺本都。米特拉达梯又在黑海西北岸现乌克兰、摩尔多瓦、罗马一带扩展影响,同此地区的萨尔马特人、斯基泰人、色雷斯人等部落结成联盟。这样,本都几乎控制了环黑海周边地区。
米特拉达梯五世去世后,本都因内乱几乎丧失了小亚细亚的所有属地。本都东邻小亚美尼亚和西边的加拉提亚、帕弗拉哥尼亚都脱离了本都,成为独立国;弗里
基亚并入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原帕加马王国)。当时,罗马在西亚除亚细亚行省外还有西里西亚行省(两省都在土耳其境内)。罗马势力在小亚细亚不断膨胀,当地的大、小王国都被罗马控制。
为争夺卡巴多西亚(在土耳其中部)对抗罗马,米特拉达梯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亚美尼亚国王提格累尼斯二世。公元前93年,本都王指使自己的女婿亚美尼亚王出兵卡巴多西亚;罗马则指令西里西亚行省总督苏拉干预。苏拉(Sulla公元前138—前78)是罗马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后成为罗马独裁官,大权独揽。他遵照罗马指令,迅速击溃亚美尼亚军队,兵临幼发拉底河畔,这是罗马军团首次进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二)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本都和罗马在今土耳其等地争夺激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89—前84)。当时,罗马在小亚细亚有步兵十二万人,骑兵一万二千人,其中罗马军团占小部分,大多数是从当地征集的同盟者军队。罗马盟国俾泰尼亚(黑海南岸,在土尔其西北部)国王尼科美德斯三世有五万步兵和六千骑兵。米特拉达梯六世有由各民族组成的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四万,另有其子阿卡提阿斯指挥的小亚美尼亚骑兵一万人,以及战车等军事装备。本都还调动了四百艘战舰。
数量占优势的本都军很快击败了罗马和俾泰尼亚联军,罗马军队节节败退。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居民把本都王视为“解放者”,许多城市的居民逮捕了罗马长官,打开城门欢迎本都军队。小亚细亚除西南一隅之外都落入米特拉达梯之手。
本都王向各城市下达密令,屠杀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据史料记载,被杀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达八万人之多,由此可看出当时欧亚各地各民族杂居的大致情况。
米特拉达梯把国都从锡诺普(位于今土耳其北部,黑海海滨的城市)迁至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滨的帕加马(Pergamum,今曼尼萨Manisa)。本都军队渡过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经色雷斯进入马其顿,希腊除伊庇鲁斯外,都处在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控制下。到前87年,罗马几乎丧失了所有东方属地。
公元前87年,苏拉率罗马军队反攻,击败了本都军队,夺回了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又倒向了罗马。前85年,米特拉达梯和苏拉缔结和约,本都接受了罗马的一切条件:退出战争中征服的一切地方,交出舰队;赔款3000塔兰特[1塔兰特talent=3600美元(1942年)]。
米特拉达梯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依然控制着黑海周围的相当大的地区。公元前83—前82年进行了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在苏拉的干预下双方恢复了和平。
(三)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74—前63年)
米特拉达梯六世镇压了博斯波鲁斯起义,扩军备战,按罗马方式改组军队,从“野蛮人”部落中招募大批士兵,建成有十四万步兵和一万六千骑兵的大军。他寻求反
罗马同盟者、和罗马西班牙总督及地中海海盗建立了关系,打算东西夹击罗马。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前74—前63年)的导火线是俾泰尼亚(位于黑海南岸,土耳其西北部)问题。俾泰尼亚是罗马忠实的盟国,其国王尼科美德斯三世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王国赠送给罗马。俾泰尼亚和本都相邻,米特拉达梯怕罗马因得到俾泰尼亚而实力大增,危及本都的安全,以俾泰尼亚王位继承者保护人的名义向罗马宣战,击败了罗马人,占领了俾泰尼亚。本都人又攻入和俾泰尼亚相邻的罗马亚细亚行省,几乎占领了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沿岸。但是,罗马统帅卢库卢斯迅速扭转了战局、收复了失地、夺回了俾泰尼亚,攻入本都。
米特拉达梯逃到亚美尼亚,向自己的女婿提格累尼斯二世求援。亚美尼亚王支援本都王,导致罗马军队进入亚美尼亚,并击败了亚美尼亚军队。但罗马军队也出了问题,士兵们对征途艰险和军纪严苛极为不满,几乎哗变。卢库卢斯不敢继续攻击敌人、扩大战果。关键时刻,罗马民主派上台,罢免了卢库卢斯的司令官职务。米特拉达梯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施反攻,回到了本都。
公元前66年,罗马任命庞培为司令官,指挥米特拉达梯战争。庞培攻入本都,本都王主动后撤,庞培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追上了本都军并将其击溃。本都王率残部仓皇逃入亚美尼亚,其女婿提格累尼斯二世见势不妙,拒绝接纳自己的岳父。米特拉达梯狼狈逃入黑海东北岸的博斯波鲁斯王国(在今俄罗斯境内)。本都王的儿子掌控着博斯波鲁斯王国政权,他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和罗马结盟。
米特拉达梯到博斯波鲁斯王国后处决了背叛自己的儿子,夺得了政权。米特拉达梯制订了一个宏伟的战略计划:联络黑海北岸、多瑙河流域、高加索各部落,组成联军,沿欧洲内陆远征,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攻入意大利。为实现此计划,米特拉达梯对占领区居民搜刮勒索,横征暴敛,引起了克里木半岛(现属乌克兰)、黑海东北岸城市起义。米特拉达梯的儿子法那西斯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
米特拉达梯走投无路,饮恨自杀。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3年,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享年约68岁。米特拉达梯六世的遗体由其子法那西斯交给了庞培。庞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安葬在土耳其锡诺普王室墓地中。
米特拉达梯战争以罗马辉煌的胜利告终。庞培把俾泰尼亚和本都的大部分领土组建成罗马行省,把博斯波鲁斯王国交给米特拉达梯六世之子法那西斯统治,并授予他“罗马人民的朋友和同盟者”的称号,本都国灭亡。
八、庞培在东方的功业
庞培利用米特拉达梯战争,为罗马占领了大片领土,把罗马的统治范围推进到亚洲的幼发拉底河和埃及边界。他消灭了本都国,将其领土变为罗马行省;他消灭
了古老而强大的塞琉古王国,变其领土叙利亚等地为罗马行省。他使罗马控制了巴勒斯坦、伊伯利亚(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等东方国家。他任意更换国王,把忠于罗马的人扶上王位,给他们增加领土,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他恢复一些被征服民族的自由,使他们成为罗马忠实的盟友。把忠于罗马和自己的异族王公权贵列为罗马人的朋友,赏给他们王位、领土和金钱。他任意干涉各国事务,成为东方各国的“王中之王”。他在战略要地和形胜之地修建新城,修复被天灾人祸毁坏的著名建筑。这样,罗马赢得了许多东方民族的同情和支持,积极参与罗马的各种事业。
庞培在亚洲还击败了科尔基伯人、阿尔巴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伊伯利亚人(格鲁吉亚人)等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他还击败了米提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其他东方民族。他直逼埃及边界,使埃及国王恐慌,献给他奇珍异宝,给庞培的全部士兵发放奖金,制作了崭新的军服。埃及国王请庞培出兵埃及,帮助镇压叛乱,但庞培拒绝了,令人费解。
庞培在战争中获得大量的财宝和战利品,他按罗马人的习惯,大赏部下,每个士兵获得大量奖金,军官则按级别翻倍赏赐奖金。
公元前62年,庞培率罗马军队到以弗所,由此登船驶向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受到热烈欢迎。庞培在勃隆度辛遣散了军队,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匆匆赶往罗马,罗马人像过盛大节日一样,夹道欢迎伟大的将军凯旋。元老院把“伟大的”称号授予庞培,从此他被称作“伟大的庞培”。
九、罗马军团的民族构成
从本文所列史料看出,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到西亚和欧洲居住着印欧语系各民族,他们起源于远古时期生活在里海和咸海一带的印欧语系部落。
远古时期的先民,过着以采集和游牧为主的生活,不经意间就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古代先民迁徙的情况不可能留下翔实的文字史料,但我们从考古发现和神话故事中可窥知一二。如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赫克勒斯完成了十二件伟大的功业,他曾到阿富汗一带攻城略地;希腊酒神巴克科斯出生于印度,曾长期在印度和阿富汗生活。可见,远古时期,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人曾返回过他们的古土中亚,反之,有些希腊人的出生地在印度、阿富汗等地,这和历史记载相吻合。
根据亚历山大随军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的记载,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说,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马其顿等希腊联军在阿富汗的乌浒河(锡尔河)流域,途经一个有城墙的小镇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当地的居民讲的是希腊语。他们自称是希腊爱奥尼亚人的后裔,祖先是看管迪狄马著名太阳神神庙的教士家族的布兰契戴。可见远古时期中亚的人到了欧洲,欧洲人则迁到了中亚、阿富汗等地。
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等大小国家的统治者都执着地想建成一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这仅仅是统治阶层野心的反映吗?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从波斯帝国到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五百年里,从中亚到西亚、欧洲、北非的各种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大帝国的版图内。有远见的统治者鼓励和支持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各种文化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接近中国的阿富汗、索格狄安那(康居或粟特)等国人民,由于战争等原因移居到西亚、欧洲等地,而希腊等欧洲居民和西亚人民则迁徙到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并在定居地生息繁衍,世代不息。如原在中亚的土库曼人现在分布在从中亚腹地的沙漠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广大地区,而谁又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土库曼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呢?
罗马共和国起源于罗马城周围的一些部落联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兴盛时期,意大利人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罗马共和国从来没有一个人口占全国绝大多数的统治民族,罗马共和国一直是一个各民族的大联盟。
罗马共和国从罗马周围的弹丸之地发展成地跨欧、亚、非的千年帝国,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占国内人口少数的统治民族怎样巩固政权并不断扩大领土。罗马统治者很高明地不断扩大国家领土的奥秘应该就是以战养战、以老异族人征服新异族人,这样,整个国家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随着雪球的不断滚动,新的雪粒成为雪球的组成部分,随着雪球的滚动,雪球的体积不断增大,外围的雪粒逐渐成为雪球的内层。
由主体少数民族和统治民族组成的罗马军团,联合相邻的异民族攻击相邻的另一些异民族。这种民族战争有时十分惨烈,死人很多。
罗马军团一旦征服了新的异民族,便对他们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让忠于罗马的上层统治者继续统治原领地,让他们实行自治等。逐渐给他们公民权,吸收他们参加罗马军团等,利用新征服的异族,再去讨伐尚未臣服的异民族。罗马人也将激烈反抗的异族人士贬为奴隶。但随着时间的消逝,奴隶成为自由人,成为公民,成为军团战士,成为军官和官员。异族人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和中坚。到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高卢人、斯拉夫人的奴隶参与作战,成为高级将领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皇室成为“蛮族”雇佣军首领的傀儡;有些“蛮族”雇佣军首领干脆将皇帝杀死,由自己取而代之。由此可见“蛮族”在罗马国家的实力和受重用的情况。
史料记载,恺撒在西班牙、高卢等地作战时,经常征召当地居民组成协防军,配合罗马军团作战。恺撒亲自从高卢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等民族中选拔骑兵,条件是各部落出身高贵者和作战勇敢者。恺撒给作战勇敢的高卢、日耳曼等民族的战士赐赏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和财物,使他们从贫寒之家一跃而成为大地主。重赏之
下,必有勇夫,许多刚刚被征服或正在和罗马军团作战民族的优秀青年积极帮助和参加罗马军队。
西班牙提提乌斯两兄弟因忠于罗马和作战勇敢而被提拔为第五军团军事护民官,恺撒曾提名其父任元老院元老。
恺撒执政时改组元老院,将原有的600位元老增加到900人。新增成员有罗马商人、意大利杰出市民、军官和军人,也有人出身于奴隶。罗马贵族看到高卢人的首领们成为元老院元老并参与国家政事时大感惊叹,表示强烈不满,一时间,讽刺的对偶句流行于罗马:“恺撒谆谆善诱高卢人民,然后把他们护进元老院;高卢人脱去他们的裤子,套上元老院议员的外袍宽边。”
罗马人征战之际,在就近向行省招募当地各民族的民众入伍,或组建辅助部队,帮助罗马军团作战。若需海军,则从全国各地调动舰只,各地以地区为单位提供一定数量的舰只,其船员由当地人组成。
庞培长期在亚洲等地作战,他按照罗马习惯在部队所到之处征兵。从米特拉达梯战争可知,庞培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今日的俄罗斯境内、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地作战并补充兵员。史料记载,庞培军中有些军团从罗马殖民区征召人员编成,有些军团由逃亡奴隶和地方协防军组成。
有些地区的部落酋长、国王带着自己的军队主动参战,帮助罗马军团。
克拉苏远征帕提亚之际任叙利亚行省总督。这里是塞琉古王国的中心统治区,再加上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对叙利亚的长期统治,这里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几乎包括当时从阿富汗、印度、西亚到欧洲的一切民族。克拉苏在叙利亚补充了大量兵员。克拉苏远征帕提亚从意大利渡海以及横渡底格里斯河之际,遇到恶劣天气,兵员损失极大,他从西亚地区招收兵员弥补军队损失。由于克拉苏从意大利带来的军队自身构成民族成分复杂,已有了大量西亚战斗人员,加之到达叙利亚的补充兵源及征战帕提亚时由周边地区的征召,可以肯定帕提亚之战罗马军团的主体构成是西亚人种。
罗马军团早期编制较小,每军团仅4500人,后来扩编为6000人。罗马军团早期只配备骑兵300人,直到公元前105年以前,罗马军团的骑兵由罗马公民组成。后来,尤其是历次战争以后,骑兵完全由外籍人员组成,原因之一是罗马人骑术不精,在马上战斗力极差。罗马骑兵以日耳曼、高卢骑兵最为精锐。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骑兵战斗力很强,参战的努米底亚骑兵就多达七千人以上,他们骑马不配缰绳,十分骁勇。骑兵中不乏西亚籍士兵,如高加索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小亚细亚人、伊朗人等。甚至帕提亚(安息)骑兵和弓弩手也参加到罗马内战之中。关于罗马军队的民族构成一来史料零散,二来古代民族十分复杂,如日耳曼人中就
有十余支,十余支名称,本文不便一一列举了。
由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数百年的统治,加上古代的欧亚大陆上战乱不休,欧亚大陆间经常发生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现象。小亚细亚、西亚、高加索、土耳其、伊朗、色雷斯、希腊等地位于西亚到欧洲西端的中心部位,欧亚各民族在上述地区杂居、融合。后来,色雷斯、西亚、高加索、伊朗、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又在罗马共和国版图之内。所以罗马帝国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几乎包括当时欧洲、西亚大陆的所有民族。
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大夏(阿富汗)人、康居人(索格狄安那人)移居到叙利亚、小亚和黑海沿岸。这样罗马军团也有一些伊朗、康居、高加索等地区的血统。但据历史记载,这三大帝国人侵中国的企图都未能实现,如果说有一支罗马军团曾在汉时被安置在河西,并定县名为骊靬之说成立,那么移居到中国的骊靬人的血统更为复杂,现在他们除中华民族各民族的血统外,还应有西亚及意大利血统。
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以基督教约翰王传说为例
姬庆红
约翰王(PresterJohn)是一个12至17世纪期间欧洲教会和诸侯所熟知的名字。他的传说因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的一封署有这个名字的信件而在欧洲风行。该信称约翰王统治的地区物产丰饶、子民和谐,并承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基督教对付敌人。该信件自问世后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先后出现了德、法、英、拉丁等语言的100多个抄本。约翰王及其传说影响深远,甚至在哥伦布以后多年仍能唤起欧洲人的热情。当然,约翰王的传说确有些荒诞不经,但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去考察,便可发现,它反映了中世纪西方人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对美好社会追求的内在价值。一、约翰王及其信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亚洲在欧洲人的印象中只是一张充斥着想象和传说的地图。有关约翰王的传说便是其中之一。最初,欧洲的朝圣者和旅行者把名字及其故事传人欧洲:在遥远的中亚,有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其统治者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长老——约翰·普里斯特,是《圣经》拜见圣婴耶稣的东方三博士的后裔。他在中亚所向披靡,声名显赫,俨然拥有着一座域外的上帝之城。1145年,德国主教奥托在其著作中提到,一位叙利亚主教亲口向他讲述了这位基督教约翰王的故事,说他打算到耶路撒冷与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并肩作战。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署名“约翰王”的信。信中介绍了约翰王的显赫地位、财富及其对基督教的虔诚,引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兴趣。这封信迅速被译成12种以上的欧洲文字,人们争相传抄和阅读。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约翰回了一封,并派遣了曾到过东方的医师菲利普(Philip)作为信使。①
当时,欧洲的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家对约翰王及其王国纷纷进行猜测。一部分人认为约翰王在印度,这可能是把他与传教士圣·托马斯混淆了。另一些人认为约翰王国应位于中亚某个未知地区的中心。上述猜测的依据是这两块地区分布有涅斯托里教派和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组织。不过,到14世纪,大部分欧洲学者已放弃了该王国在亚洲的猜想,而认为它在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王国。到16世纪末时,约翰王出现在荷兰人和德国人绘制的南部或东部非洲地图上。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德国学者为首的国际学术界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迄今不衰。概而言之,关于约翰王及其信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约翰王人物原型的研究。约翰王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已久。马可·波罗认为,蒙古草原部落克烈部首领王罕脱里才是真正的约翰王。1322—1328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岛中国旅行,把汪古部的首领当作了约翰王,并指出以往关于约翰王的种种传说不足为信。①研究该问题的先驱学者古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和弗雷德里希·赞克(FriedrichZarncke)认为,约翰王就是中亚Qara-Khitay帝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②鲁布鲁克认为,约翰王是指乃蛮部的屈出律。俄国学者布鲁恩(Ph.Bruun)于1976年提出,约翰王应在格鲁吉亚中寻找,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格鲁吉亚正在经历对穆斯林势力形成挑战的军事复兴。③M.巴伊兰(M.Bar-Ilan)则认为,约翰王信中的约翰居住在印度,而不是埃塞俄比亚。④1923年,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马里涅斯库(ConstantineMarinescu)认为约翰王的原型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1931年,意大利学者李奥纳多·奥勒斯吉(LeonardoOlschki)另辟蹊径,首先提出约翰王传说只是乌托邦。他相信,约翰王及其信件并没有历史原型,根据地理寻找他的王国毫无用处。此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如有人认为这个传说是混合了某些放纵诗人与朋友取乐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当代研究者已经放弃了固执一说的做法,而更注重对该传说历史演变的考察,例如大卫·摩尔根(DavidMorgan)考察了13世纪期间约翰王“候选人”的变化过程。⑤
第二,关于约翰王传说缘起的研究。关于该传说产生的根源,学术界的观点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寻找基督教盟友。约翰·拉纳(JohnLarner)认为,约翰王的传说表达了西方人寻找对付穆斯林的天然联盟的一种强烈愿望。①中国学者吴莉苇也认为,十字军东征时期凡有远东的军队攻打穆斯林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涉及的地理区域都被编入约翰王的故事中,那些穆斯林的敌人们就被基督徒设想为约翰王及其臣民。②瓦西里耶夫(A.A.Vasiliev)也指出,约翰王的信件于14或15世纪在俄罗斯流行也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盟友,以消除鞑靼人的威胁。③ 第二,欧洲神权与世俗权力之争的需要。例如,汉密尔顿认为,该信件是德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Barbarossa)差人伪造的,是他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斗争期间宣传的组成部分。④
第三,借以改善欧洲基督教社会道德状况。李奥纳多·奥勒斯吉认为,欧洲人虚构约翰王的目的是表达对当时欧洲基督教分裂状况的讽刺,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其目的在于改善欧洲人已经败坏的社会道德。⑤ 第三,该信件作者身份的研究。由于该信件出现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人认为约翰王“部分上是十字军想象世界的一个产物”,即此信作者应为基督教会的教士。李奥纳多·奥勒斯吉也认为其作者是西方教会的一个牧师,但他在信中只是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M.巴伊兰认为约翰王之信的作者是中世纪意大利的犹太人。⑥伯纳德·汉米尔顿(BernardHamilton)将其视为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为政治目的伪造品,可能由费雷德里克国王的大法官,科隆的大主教莱纳德·冯·达赛尔(Rainaldvon Dassel)炮制而成。⑦国内的龚缨晏先生运用中国古籍与国外学者长期研究成果相对照,对各种观点给予了评述,但并未表示支持其中的一种。⑧
二、中世纪西方对约翰王的“寻觅”
(一)雾里看花:11~12世纪,印度神奇的约翰王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西方的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为了巩固和扩大天主教的势力,极力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地中海东岸国家和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企图建立“世界教会”。然而,阿拉伯国家此时势力已经壮大起来,并对西方世界构成强大的威胁。尤其是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SeljuqTurks)占领了耶路撒冷,对教皇和基督教世界打击很大。欧洲人渴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但是多次十字军东征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成果,加之罗马教皇与欧洲各君主争权夺利,使整个欧洲社会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
于是,他们开始寄希望于在穆斯林世界的东面能有同盟者,约翰王的故事也就不胫而走。约翰王的原型可追溯到《新约》中的“约翰王”的提法。①在传入欧洲之前,约翰王的故事也许在亚洲的聂思脱里教派中流传已久。1122年,一名自称来自印度主教约翰(PatriarchJohn)到达罗马,要求教皇承认他的职位。这名主教约翰声称,自己所在的胡尔南(Hulna)城建在婆黑森(Phison)河边,规模和势力很大,虔诚的基督徒居住其中。城市外,十二僧侣为了纪念十二圣徒修建了圣托马斯大教堂,在他的斋戒日全亚洲的基督徒都来参观。②对此,约翰·拉纳表示:“我们面对的不过是某个自信的骗子,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制造出把戏糊弄教皇。”③ 但是,这个在东方影响力很大的基督教团体的故事还是被传播开来。
最早一份关于约翰王的记载见于德国弗赖辛(Freising)的奥托主教(BishopOtto)1145年发表的《编年史》。奥托声称亲自见到来自安条克公国的主教休(BishopHugh)向罗马教皇尤金三世(PopeEugeniusⅢ)报告说,在世界的最东方,有一名国王兼长老的约翰,是基督教徒,是《圣经》中的古代东方三博士④的直系后裔,曾打败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穆斯林国王塞米阿第(Samiardi)兄弟,并攻占了其都城埃克巴塔那(Ekbatana)。他受到祖先的激励,想到圣城耶路撒冷朝拜,但因军队无法穿越底格里斯河而退兵。根据学者的研究,休提到的这场战役可能是1141年哈喇契丹(1124—1211年,即西辽帝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Yeh-lüTa-shih,1094—1143年)与塞尔柱苏丹桑贾尔(SultanSanjar)在中亚河中地区卡特万(Oatwan)的会战,结果后者战败导致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这块地区。而耶律大石的突厥语称号“葛儿罕”(汉字又译作“古儿汗”、“菊儿罕”等),读音后讹传为希伯来文的Yohanan或叙利亚文的Yuhanan,由此再转化为拉丁文的Johannes或John。①经学者考证,耶律大石本人并非佛教徒,而是萨满教或后改信佛教徒,因而休提到的约翰王误以为是耶律大石②,但耶律大石统治部落中确有涅斯托教徒。
在1165年,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收到一封没有地址的“约翰王之信”。这位约翰王首先声明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城中的基督教徒处处受到保护”,但也有不少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民。其次自己的王国疆域广大,“统治三个印度”,“如果您确想知道我的权限范围的话,那么请您坚信,我,约翰·普里斯特的统治至高无上,其美德超群,我十分富有,统治着天下的万物生灵。” “地上蜂蜜流淌,处处都有牛奶”,“到处有着奇珍异宝”。皇宫金碧辉煌,“采用圣托马斯为King Gundoforus设计的模式建成”,经常用隆重盛大的宴会款待子民。“在这里没有做伪证者、货币伪造者、私通者或强奸者”。最后,讲述国内神奇事物。城内有亚历山大之门(theGateofAlexander)和不老泉,有一个魔镜能够看到自己统治区域的任何角落。
由此来看,约翰王及其传说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是欧洲人在没有使者或传教士亲自到亚洲考察前对东方的想象,其中的“错误”自然难免,例如信中所谓的“三个印度”③,以“近印度”向东最为突出。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印度就是世界的最东方,约翰王就是东方的统治者。这种想象很可能是根据亚洲的聂思脱里教徒或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道听途说的亚洲战事,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军事的失利需要外部帮助的需求下产生并广泛传播的。
(二)犹抱琵琶:13~14世纪,中亚草原上的约翰王
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大军的西征使东西方的碰撞与认知成为可能。随着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顺利进行,基督教徒占领了兄弟国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暴露了罗马教皇积极寻求对已知世界的封建君主的权位争夺,而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在黑海和其他东方地区“发现”了更多的基督教徒,并错误地认为穆斯林世界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超过了穆罕默德的信仰者。这无疑激发了罗马教皇更大的野心,也更加使欧洲人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位皈依基督教的约翰王将会帮助他们取得尘世和精神的巨大胜利。
13世纪初,蒙古人的迅速崛起与对外扩张是西方人始料未及的。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三次西征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对于这个彪悍、野蛮的可怕民族,西方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并企图到他们中去寻找梦寐以求的约翰王。
1221年,随十字军东征至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巴勒斯坦的阿克雷主教(BishopofAcre)德维特里(JacquesdeVitry)和西部教会的佩拉吉斯枢机(Cardinal Pelagius)向罗马报告说:“两个印度的国王”大卫王正率领着彪悍的军队帮助基督教武士们,并吞掉了强大的撒拉逊国。他是约翰王的儿子或孙子。①其实,他们所指的大卫王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因为后者在1219—1222年间攻灭了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花刺子模(Kharezm),并占领了波斯东部的呼罗珊诸地。这让欧洲的基督教徒们群情激昂,更加坚信约翰王的存在,并将之视为攻打穆斯林的天然同盟。
1240年前后,蒙古人的铁蹄踏进欧洲,使欧洲人关于约翰王的美梦变成了歌各和玛各的噩梦。其实,最早意识到蒙古人威胁的是穆斯林异端亦思马因人。他们在1238年曾向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建议结成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大同盟共同对付来自东方的可怕敌人。但是,这一建议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当时西欧教俗权力之争,尤其德皇腓特烈一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根本无暇顾及尚未成为重大威胁的蒙古人;同时蒙古人对穆斯林世界的打击,让欧洲人乐于坐山观虎斗,想渔翁得利,让“全球变得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基督”。
拔都第二次西征,饮马多瑙河,里格尼茨打败西波联军。这使西方世界惊慌失措,各种猜测随之产生。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Paris)满怀恐惧与憎恨地称,蒙古人就是《圣经》中预言的来摧毁基督子民的歌各和玛各的后代,他们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 。他认为,这也许是上帝假鞑靼人之手来惩罚他们的罪过。
与此同时,教皇格里九世呼吁组织十字军抵御蒙古人。但是,由于德皇与罗马教徒互相攻讦而流产。③1245年,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集中讨论如何防止蒙古侵略的问题。一面对防御工作,一面派遣教士充当使者,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戮基督教和侵犯欧洲,并企图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随后,罗马教会和国王纷纷派遣传教士前往寻求约翰王。其中有著名的博朗·嘉宾、阿西林使团、路布鲁克等人出使蒙古,尽管结盟的使命没有完成,但他们得知蒙古人中有不少聂斯托里教徒,使得欧洲人依然坚信在鞑靼人和穆斯林所构成的屏障以外存在约翰王的国度。
在此期间,1241年窝阔台大汗病逝,致使在欧洲征服的王子们抽兵回国,西征暂时停止。此后,蒙古人再也没有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攻势。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噩梦。于是,他们编造出各种说法来描述他们是如何打败和赶走了蒙古人。1253年,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摧毁巴格达和叙利亚,让基督教世界一片喝彩。蒙古人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认为蒙古人是伊斯兰教的天敌,是上帝的意志让穆斯林招致灭顶之灾。但是,蒙古人对待欧洲的反复无常,让他们相信,蒙古人肯定不是他们所期盼的约翰王。
在此背景下,马可·波罗的叙述充当了确认歌各和玛各之地与约翰王之国地理位置的重要角色。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从六十三章至六十七章、七十二至七十三章节中都涉及约翰王的问题。①其大体内容如下:1.鞑靼人确实是居住在北方的玛各人②。但歌各与玛各之地曾被约翰王③所征服,但现在约翰王的国土又被鞑靼人征服。2.可汗宽容那些不反对帝国臣民的各种信仰,因基督教徒战前占卜成吉思汗取胜,故优待基督教徒。3.鞑靼人与约翰王之后联姻,如成吉思汗纳王罕之女为妾,四子拖雷娶一女。而约翰国王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公主为妻。
尽管马可·波罗在该问题认识上出现了不少史实性错误,但他为鞑靼人和约翰王这原本敌对的两族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约翰王也不再是传奇中战无不胜的英雄,而是被蒙古人打败的真实人物。最关键的是,马可·波罗认为,契丹是鞑靼人统治的约翰王之旧地,并仍有众多基督教徒生活其中。④而且,在契丹南面是居民为偶像教徒的蛮子国。⑤这使得欧洲人对“大印度”之中的“近印度”多了一些具体的知识。但在蒙古帝国瓦解后,欧洲人开始动摇这个念头:约翰王是否确实是中亚大草原上的某个国王。⑥随着13世纪末天主教派来到元朝,聂斯托里派在大草原上的历史逐渐结束,约翰王及其传说也随之淡出亚洲。
(三)蓦然回首:14~18世纪非洲的约翰王国
蒙古作为一个霸权国在亚洲的兴起以及商业在欧亚世界体系中的扩展,西方人开始意识到最遥远的亚洲内地与约翰王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是,欧洲人很快为他在未知的和神秘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个新家。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除了欧洲人对亚洲约翰王的幻想破灭外,埃塞俄比亚从4世纪开始就是一个传统基督教国家。自从约翰王的传说开始,欧洲人就认为他统治着三个印度,但他们对“印度”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模糊的。约翰王之信的作者由于缺乏对印度洋的基本知识,把埃塞俄比亚看作三者之一。当时的西方人就知道埃塞俄比亚很早就是一个基督教民族王国,但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欧洲与它的联系非常少。
其次,认为约翰王应在埃塞俄比亚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宗教认同。在中世纪晚期,耶路撒冷是欧洲与非洲之间三大交流地区之一(其他两个是南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随着十字军控制了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东方基督教文化的净土” 的城市(1099—1189年,1229—1244年),该城市受到各派督教的关注,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派。在这个教派林立的城市,十字军是否可以首次代表着基督教跨越洲际的自我觉醒还在争论之中。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地位代表着不是以种族认同而是以宗教为枢纽对“他者”的认识。①1244年耶路撒冷重新陷落后,埃塞俄比亚被欧洲人处心积虑地继续解释为欧洲以外反穆斯林战略的中心舞台。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要求约翰王重新团结在天主教会的旗帜之下,并在1300年为基督教协定拟订了计划,包括“亲爱的努比亚和上埃及其他国家的黑肤基督徒”。②
最后,还与该时期埃塞俄比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有着直接的关系。13世纪后半期,在十字军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期间,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所谓的所罗门复兴时期——扎格维王朝(Zagwe,1137—1270年)时期。其前几代君王,如耶库努·阿姆拉克(YekunoAmlak)、雅各布·塞容(YagbeSeyon,1285—1294年)等励精图治,壮大了军事实力,并加强了宗教力量,随后在东非高原实行了连续的扩张和巩固政策。强盛时期,扎格维王朝时期,基督教已经战胜了世俗权力,其统治的领域甚至超过了阿克苏姆极盛时期,并重新夺回红海贸易权。
鉴于以上原因,欧洲人在埃塞俄比亚为约翰王安置新家,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1306年,30个埃塞俄比亚大使被皇帝威德姆·阿拉德(WedemArad)派往欧洲打开了双方之间的外交来往。在他们被询问的记录中,提到他们教会的主教叫作约翰。第一个清楚描述非洲长老约翰王的是,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士约旦努斯 (Jordanus)于1329年发表的《趣闻集》中。当讨论“第三个印度”时,他记录了不少非洲大陆和国王们的趣闻逸事,并说欧洲人把他们叫作长老约翰王。③从此,非洲约翰王国的说法流行开来。
1487年和1507年,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互派使者。欧洲人加强了对非洲埃塞俄比亚的直接认识。1520年,埃塞俄比亚皇帝莱伯纳·邓格尔(LebnaDengel)与葡萄牙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这期间,约翰一直被欧洲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名字。有学者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说,埃塞俄比亚的宗教语言和上层语言中“国王”或“陛下” 可以写为Zān、ān或者ān,其发音有些像法语中的“Jean”或者意大利语中的“Gian”,都是指John。埃塞俄比亚的主教就是国王或者Zān。①尽管如此,但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人从未这样称呼自己的皇帝。
当皇帝扎拉·雅各布(ZaraYaqob)的大使于1441年参观佛罗伦萨时,当议会的高级教士坚持说他们的国王就是约翰时,他们感到很疑惑,并试图解释在一系列皇帝的名单中就没有出现过这个称呼或头衔。②然而,他们的警告没有阻止欧洲人继续这样称呼他们的皇帝。此后多年里,埃塞俄比亚都被认为是长老约翰王传说的起源地。欧洲人一厢情愿的做法是因为满足外部基督教盟友的宗教情感的需要。埃塞俄比亚是远印度或近印度,或者是第三个印度,对于欧洲人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它是基督教盟友即可。现代学者在古代资料中找不到约翰王及其国家,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也有说服力地证明,在与欧洲正式接触前,这个传说并不为埃塞俄比亚人所熟知。其实,早在18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曾否定了自己是约翰王或叫约翰的说法。捷克方济各会雷米蒂·普鲁特科(RemediusPrutky)于1751年问及皇帝伊雅苏二世(Iyasu Ⅱ)这个说法时,皇帝很吃惊,并告诉他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从不习惯自己这样被称呼。③这应该是由埃塞俄比亚君主来回答欧洲人这个传说的首次记载。当被想象的“他者”亲自站出来,澄清“自我”的真实身份时,再固执的想象者也该恍然大悟了。此后,这位神奇的约翰王只能脱下历史的外衣,进入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发挥“全能至上”的本领了。④
三、余论
从12世纪至14世纪,欧洲对约翰王的认识经历多个人物原型的变化,对其领地位置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印度到中亚,再到非洲的转换,最后只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个转换历程清晰地反映出西方对东方的认知由模糊状态中的完全想象,到逐渐修正为部分想象,最后到认识清晰下的想象褪色、消失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说,约翰王及其传说是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将东方作为他者,根据自我需求构建东方、臆想东方的结果。但是,约翰王的传说又并非子虚乌有,正如查尔斯·E.诺维尔所说,约翰王的传说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方传说与真实历史事件奇妙的调和物。①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作了长期大量的努力,探讨约翰王(或信件)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结果仍无定论。他们论争的出发点是传说或传闻与“历史事实”不能相容。然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追求绝对真实不同,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事实背后的真相。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待该问题,即是否可以把它看作中世纪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在浪漫化异域的同时,追求一种政治地理的知识,是“幻想地理”和“真实地理”的综合体。②也许约翰信件本身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表达某种观念,或描述某个真实的地理区域,而是让理想世界和现实政治观念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叙述出来。约翰王信件对其王国的描述俨然是人间天堂或上帝之城,充满着美德、正义与和谐,远优于12世纪西方腐败的基督教世界,其实这是基督教的普适主义理想的境界和象征。只不过因现实残酷的宗教斗争,这种对东方异域的浪漫化想象被西方人企图纳入自己斗争的“阵营”当中来,而少了些美好和高尚,多了些世俗和污点。
约翰王无论作为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传说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教会分裂、教俗权力之争以及十字军东征失败的年代,约翰王似乎成为了驱除伊斯兰教的象征并使欧洲人精神上有所寄托。因此,从12世纪直至美洲发现后,这个传说甚至成为欧洲思维模式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作为穆斯林后方的一个潜在的基督教盟友,为后来十字军的行动计划提供了参照,因而在欧洲的世界战略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约翰王的传说引起了欧洲人对未知领域的积极向往,刺激了欧洲君主们对海外探险的兴趣,从而推动了理大发现的到来,因而约翰王的传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几个问题①
丁得天 高倩
刘萨诃,法名释慧达,东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高僧,其事迹在佛教典籍、碑记、石窟壁画、民间信仰和传说中多有记录,广为流传。国内外学术界对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探讨已经持续了近百年的时间,[1]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台湾佛教史学者陈祚龙先生著文开始,又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2]至今仍尚未停息,且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其不仅在佛教信仰、史籍、文物考古、美术史、图像、民族及敦煌等学术领域有热烈的讨论,而且在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亦有全新的探索。诸位前贤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硕,只能望其项背。笔者自不敢班门弄斧,而是因较为熟悉金昌的历史和地理概况,又对圣容寺及番禾瑞像颇感兴趣,对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问题也略有一些思考,囿于所学,故此求教于方家。
一、相关的文献记载
刘萨诃及其事迹,正史和佛典都有收录,材料比较丰富,如南朝王琰的《冥祥记》,梁慧皎《高僧传》,姚思廉《梁书》,唐初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释迦方志》,唐释道世的《法苑珠林》等都列其事迹。刘萨诃,或称萨荷、萨何、萨河、摩诃等。其民族属性在各类典籍中记载是比较一致的,都是稽胡族,是包括匈奴、胡人以及当地土人的“杂胡”。[3]南北朝时活动于今陕北、山西西北部一带的山谷中,以游牧、射猎为业,后逐渐与汉族融合。关于刘萨诃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王琰的《冥祥记》中。王琰仕于齐、梁间,约生于宋孝建元年(454年)前后,幼年受戒成为佛弟子,曾游历于江都、峡表等地,齐建元元年(479年)复还京师。他在《冥祥记》中自称幼年时从贤法师处得到一尊观音金像,此像能“放光照三尺许,金辉映夺”,自得到此像以后,“瑞验之发,多自是兴”,故《冥祥记》一书不免多有离奇荒诞之事,不过其成书时间距后来故事中番禾县望御谷“授记”的时间却是最近的。
《法苑珠林》卷八十六《冥祥记》载: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将尽之时,见有两人执缚将去。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啖肉,何缘受报?”。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
《冥祥记》中之事多不可信,自然也包括刘萨诃“暴病而死”、“至七日而苏” 之类冥游、灵验的故事。不过我们从此处还是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对刘萨诃的一些认识:可能是今山西离石(今吕梁地区)人,三十一岁出家。出家之前可能是军卒。不知道有佛法,尚武,尤好田猎。得暴病却未死,七日后苏醒,醒来以后就叙述了一些他在地狱中冥游、受到点化出家、精勤福业等种种不平凡的经历。
这里需要留意刘萨诃出现的时间及其年龄。文中记载刘萨诃出现时的年龄已是三十一岁,也就是其出家时的年龄。据文中所记,出家以后他又在江东、许昌等地游化,游化了多长时间文中没有提及,太元末年(396年)仍知其在京师,由此可以推算刘萨诃至少生于366年,但依照王琰的语气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刘萨诃在江东、许昌游化的时间已不算短,生年要早于366年,再往后其行踪就不知所终了。再看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释慧达一》:
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域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先是简文皇帝于长干寺造三层塔。晋太元十六年(391年),孝武更加为三层。达东西观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厉,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慧皎乃佛教史家,其书历来为佛、史两家所重。《高僧传》中记事截至梁天监十八年(519年),成书时间较《冥祥记》略晚。从上文的记述来看,《高僧传》相较于《冥祥记》的记录更为简单平实,但多出了刘萨诃晋宁康中至京师礼长干寺、拜阿育王塔像等“东西观礼,屡表征验”之事,且刘萨诃“忽如暂死”以后,只用“备见地域苦报”来一笔带过其在地狱冥游时离奇繁复的经历,基本是叙述了刘萨诃在江东一带的活动轨迹,以及因统治者信佛而修造塔寺之类的活动。可见慧皎对这类感通、冥游之类的故事不似王琰那般重视,或者说有意做了精简,就使得可信
的成分增大了。[4]实际上,慧皎和王琰生活的时代相去不远,慧皎既要为高僧立传,必然要取其重点,略其枝节,这也是关于刘萨诃早期的事迹中相对最为可信的记录。
此处仍需留意有关刘萨诃的几个时间点,这与下文将要提及的刘萨诃西行一事是有重要关系的。刘萨诃出现时同样是三十一岁,但以375年至京师为限,当生于345年左右,比前文的推算要早二十一年,去向仍不知所终。
其后二百余年,唐初南山律师道宣的《续高僧传》又收录了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故事,《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篇”《魏文成沙门释慧达传》载:
释慧达,姓刘,名窣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字,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母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闾,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520年)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逮(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建德初(572—578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575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581—600年)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初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
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道宣的其他著作中,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等,其记载基本相同。但是,事情在这里出现了变化:刘萨诃西行求法、至凉州番禾县东北望御谷时“授记”、不久就卒于酒泉、八十余年后瑞像从望御谷出世并昭示天下离乱等一系列离奇神异的事迹。
二、刘萨诃是否到过河西走廊
道宣对刘萨诃的籍贯、生卒年以及活动轨迹提出了新的看法,今人对刘萨诃生平的巨大争议也肇始于此。从道宣的记述中第一次看到了刘萨诃西行并卒于河西的情况,且刘萨诃预言“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引用道安碑的说法也是番禾“授记”最早出现的版本。道宣关于刘萨诃的记载,是在其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搜集资料、抄录碑文之后撰写的,文末他也提到上述内容“见于姚道安碑”。这个道安陈祚龙先生有考,就是北周冯翊胡城作《二教论》的姚道安。[5]道安作《二教论》,称佛教和儒教是“外教”和“内教”,道教则依附于儒教,实际上当时道安等人的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北周武帝“法难”的到来。
王琰和慧皎的著作中并没有述及刘萨诃西行求法并在凉州番禾县“授记”一事,但其事迹却出现在二百余年后道宣的著作中,道宣也是在考察中发现了姚道安碑才转引的。从“广有别传”、“备如前传”这样的文字来看,道宣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应当是看到过慧皎等人关于刘萨诃的记载的。发生在北凉的事情没有出现在早期王琰、慧皎的记述中,却见载于唐初道宣的著作,有意思的是道宣依然坚持己见,将刘萨诃西行求法及“授记”一事在不同的著作中多次转引。道宣游历过的这些地区,刘萨诃及其信仰是非常兴盛的,并且已经流传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从文中也可以反映出。道宣同王琰、慧皎一样,没有亲自到故事的发生地——番禾县去查看过,仅从道安碑的记载和当地百姓崇信刘萨诃的盛况就确定番禾县“授记”一事,理由尚不充分。
再看前文提到刘萨诃前后出现的时间。依道宣的记载,刘萨诃于435年到过番禾县并做了“授记”,但此事缺乏可信度。首先,年龄偏大。刘萨诃在各部典籍中第一次出现时的年龄都是一致的,皆为三十一岁。若按照王琰的记载,以太元末(396年)尚在京师为限,至435年刘萨诃已年过古稀,况且文中之意其至迟在396年之前就已经到过京师了,以如此高的年龄西行求法,不免牵强;若按照《高僧传》云其“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到番禾县“授记”后一年(436年)殁于酒泉县城西七里涧为下限来算,已臻九十二岁高龄。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尚能翻山越岭,西行求法,实在难以想象,难怪陈祚龙先生也惊叹其“俗寿竟达九十有二”。而且慧皎的记述可信度要大于《冥祥记》,所以从年龄来看其西行河西一事尚不能使人信服。其次,出现和消失的突然性。《冥祥记》和《高僧传》二文记载一致,都不知道刘萨诃最后去往何处。但到了道宣那里出现了变化:“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达)流化将讫,便事西返。”也就是说最晚在太元末年(396年),时人尚能知道刘萨诃在京师或去往许昌,之后就不知所终了。在时隔近40年时间之久以后,刘萨诃突然出现在河西走廊的番禾县(今甘肃永昌县),而且没有他自东向西走过的广袤地域的记录,直接从江东跨越至河西,并且在这里做了这个从后世来看极为灵验的“授记”,他预言石崖当有瑞像出现,若是灵相俱备,则天下太平;若是身首异所,则天下大乱。此后“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又很快消失了。其时刘萨诃已是有道高僧,否则亦不会名列僧传。那么他在长达40年之久的时间里如蒸发了一般,这40年里他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史籍和内典均没有留下记载。从原来的江南、中原一带突然出现在河西走廊,地理跨度如此之大,并且在番禾县望御谷“授记”,挂锡云庄山,之后又“授记”莫高窟,之后再殁于酒泉。在河西出现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游历了这么多地方,办了这么多事,却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迁化于酒泉,着实令人费解。尚丽新先生认为刘萨诃西行求法之事本就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番禾县“授记”可能是出自河西走廊的一种传说,但没有具体说明传说的源头及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基于以上资料和论述,刘萨诃西行河西并在番禾县“授记”一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结论的成立,但它并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必然有其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三、隋炀帝改额感通寺与番禾瑞像及其信仰的流传
前文《续高僧传》载,“开皇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政权以后,大力弘扬佛教,不仅借此收买人望,还依靠佛教的一些理念来稳固其政权。且隋文帝杨坚因出生于尼寺,儿时为尼姑所养,甚至还为他取名,直至十三岁时方才还家。《隋书》(卷一)载:“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刘氏女也。及帝诞日,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割庄为寺,以儿委尼,不敢召问。帝年十三,方始还家。”①因隋文帝有在尼寺出生成长的经历,故其当政以后大力弘扬佛教是有缘由的,甚至达到了“佞佛”的程度。隋文帝的皇后等也十分崇信佛教,故开皇年间瑞像寺经像大弘是天下大势,各地的佛寺道场都很兴盛。因父亲杨坚佞佛,隋炀帝为东宫太子之时,崇信佛教也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君臣,西域各国向炀帝敬献广大土地、名马、表册等,以示顺服。而在此前,炀帝御驾亲征青海得胜后,过扁都口至河西走廊时遇到不测,其所属军马、随从等“死者十之六七”。学者多认为隋炀帝大队人马在通过高海拔且狭窄的扁都口时遇到了极端的天气,甚至考虑其是否因天气而引发了踩踏事件。虽时值夏季,但祁连山区高寒风大,亦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此处不再展开。隋炀帝是古代大一统国家中第一个亲征西域的国君,尽管其在后世的“声名”不好,称其为暴君,但不能否认其在一
定程度上开疆拓土的雄心和功绩。
隋炀帝在焉支山大会西域各国君臣后,听说了瑞像寺有这样一尊十分灵验的瑞像,甚至可以表征国家命运的兴衰,遂亲至瑞像寺。“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从“躬往”等形容词看,炀帝对番禾瑞像的尊敬和信奉程度可见一斑。既然皇帝亲自诣寺礼拜,那么“厚施”和“重增荣丽”就是必然的事情了。隋炀帝杨广甚至亲笔将原来的“瑞像寺”旧额改为“感通寺”,“感通”当即有感而通灵之意,为佛教中表征灵验常用。“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炀帝在将“瑞像寺”改名为“感通寺”之后,又令随从摹写番禾瑞像的图像造型,让各地寺院依图供养。在帝王的崇信和推动下,瑞像寺改名为感通寺,番禾瑞像的造型为各地的寺院供养,那么瑞像本身所包含的和表征的信仰也就随之而流传开来。
现存各地的番禾瑞像,不论是造像、绢画、刺绣、壁画等,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内出土和现存的造像、壁画等,大部分的时代都在隋代以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隋炀帝的推动。炀帝下令各地依图供养番禾瑞像之后,借助皇帝的权力和崇信,番禾瑞像的形象及其信仰才广泛地传播开来,甚至在入唐以后,有更加兴盛的趋势。
四、现存与刘萨诃、番禾瑞像及圣容寺相关的文物
前文已提到,关于刘萨诃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是较多的,现存于各地的相关文物资料也很丰富。
今城关镇金川西村望御谷最西边的北部山崖下,仍能看到依山浮雕的瑞像像身。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的佛首(图一),原为县文化馆馆长在该村发现,后运送至县文化馆。佛首高约67厘米,为青石所雕,与像身石质迥然不同。头顶螺髻低平,肉髻已残损,面阔方颐,高鼻厚唇。造型为早期造像,并有着“受印度造像影响”的痕迹。①依佛首比例量度,瑞像当与传说的“一丈八尺”相差不远。
20世纪80年代,于金川西村农舍发现一尊番禾瑞像造像(图二),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②造像为砂岩质,残高110厘米,宽53厘米。佛像虽残,仍能看出其轮廓造型。头光后面,左肘下至仰覆莲台之间的空白处施有红彩。此尊也是番禾瑞像的造型,其时代尚存有争议。
炳灵寺石窟下寺窟区下层南段第13龛,龛为一尖拱形龛,高139厘米,宽74厘米,进深22厘米。龛内雕一立佛像,高97厘米。龛内造像亦为番禾瑞像(图三),其时代为晚唐。
20世纪90年代,于县城西南红山窑乡青龙山庙发现有唐代青龙山石佛造像一尊,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图四)①。造像为石灰岩质地,以高浮雕、圆雕手法雕刻而成,体量较大,是为“等身佛”。背后有舟形身光,顶部已残,沿上边弧顶雕有五身小化佛。佛像高170厘米,宽85厘米,体态丰膄,与真人几近相等。低圆发髻,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捏衣角。衣服周边有锯齿状纹饰,背屏周边浮雕有嵯峨的山形。此尊正是盛唐时期番禾瑞像的造型。
另在圣容寺东临河处有一小型石窟,窟中残存有一尊北魏时期造像(图五),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造像为砂岩质地,残高114厘米,头部及膝部以下皆残去,舟形背光,上布有七身小佛,左手握衣角。②也是番禾瑞像典型的造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的第6窟为一平顶长方形的大窟,窟高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高浮雕一立佛像(图六),左右壁各雕一弟子像,为迦叶和阿难。主尊佛像高4米,水波纹高肉髻。沙武田先生认为该窟主尊立佛及胁侍二弟子像处山形中,当为凉州瑞像。但现在主尊造像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重修,已失去原有的面貌,幸得《河西石窟》记录了原来的佛像而得以辨识。
其他番禾瑞像造像还有山西省博物馆馆藏,出自山西万荣县唐开元年间的“李元封等造像”(图七),四川安岳石窟番禾瑞像③,日本高野山亲王院藏的金铜瑞像(图八)等等。此外绢画、刺绣和文献文本等主要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现在分藏于世界各地,英国大英博物馆、印度NewDelhi博物馆、法国及日本等地,此处不再赘述。
圣容寺前后山顶各有大小佛塔一座。寺后山顶大塔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图九),七级浮屠。第一层塔身较高,每边长5.44米,逐层往上收分,通高约12米。每级南面辟窗,当为通风、采光之用。塔内原有木梯通至塔肩部,后损毁。其内壁有唐“乾元元年”(758年)的墨书题记,另有“……一千五百人”、“圣容寺”、“番僧……”字样。整个塔造型简洁,外部轮廓呈轻微的抛物线,是典型的唐早期密檐式塔,与西安小雁塔形似,唯小雁塔南北两面皆辟窗,而此塔只南面辟窗。
寺前山顶小塔,亦是空心方形七级浮屠。第一层塔身较高,南面辟窗洞,东西2.13米,南北长2.26米,通高4.9米。此塔低矮,外部轮廓无抛物线,与西安香积寺善导塔外形极为相似。
五、与番禾瑞像有关的一些思考番
禾瑞像有多种称谓(“番”读“盘”),学界多称为“凉州瑞像”,莫高窟237窟榜题名为“圣容瑞像”,亦有因今之寺名称“永昌圣容寺瑞像”者,还有“凉州番禾县瑞像”、“番禾瑞像”、“刘萨诃瑞像”等,不一而足,但皆指今甘肃永昌县城北圣容寺后依山而立的浮雕瑞像,本文从“番禾瑞像”之说。
番禾瑞像有其固定的造型样式:立姿,着衣袒右肩。右手沿体下垂作与愿印,左手屈臂握住衣角,衣角长出手心,垂下的衣褶大致呈菱形,衣服边纹部分有锯齿状图形,身后背光有嵯峨的山岩,赤足立于莲台上。其中判断番禾瑞像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佛像身后是否能看到嵯峨的山岩或者类似于石崖、山峦等形状的背光。因文献记载,此像是“雷震山裂”而挺出的石像,佛像本身的背光与山岩的背景便很好地结合起来,也为番禾瑞像的造型提供了“理论支持”。
番禾瑞像的产生并非像文献中记载那般简单,也不仅仅是因为佛徒为宣扬佛教附会而“出世”,其必然是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结果。首先,地理位置的因素。番禾县扼守凉州西部,是丝绸之路和佛教东传的必经要道,有佛教传入的外部条件。“五凉”时期各路王侯争夺的目标都是“畜牧甲天下”的凉州,番禾县正是拿下凉州的桥头堡,实乃兵家必争之地,长年争战使得各个阶层都希望能安定下来,宗教就变成了人们“精神的鸦片”,佛教正好顺应了这个愿望。其次,与北凉的关系。北凉一朝,特别是沮渠氏迁都凉州以后出现了短暂的安定繁荣,人们当然不愿意回到过去。刘萨诃“授记”的北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即北凉沮渠牧犍永和三年,牧犍继位后其佛教活动比蒙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凉自沮渠蒙逊开始,就在都城凉州组织译场进行译经活动,这种大规模的译经弘法活动使得凉州也成为当时中国翻译佛经的中心之一,佛教已成为统治阶级和民间信仰的主流,大乘佛教的诸多重要经典在这里也被翻译出来,为此后大乘佛教的流行奠定了基础。435年刘萨诃在番禾县的“授记”也并非偶然发生,而明显是有意的安排,张善庆、沙武田二位先生在《凉州瑞像及其信仰的末法观》一文中也提出“末法”思想对具体年代的影响。再次,刘萨诃本人正是佛教徒宣扬佛法所需要的“榜样”。刘萨诃出家之前本是一个嗜好打猎的下级军吏,依理来看这样杀生犯戒之人业力深重,但是又似乎够不上“一阐提”,可他在“忽如暂死”以后放下屠刀,“顿悟”出家了,尽管大乘佛教的流行使得“人人皆可成佛”,但早期大乘思想的流行和不断深入人心正是由这样一个渐趋成熟的过程体现出来。再次,从统治阶层的角度看。尚丽新、杨君二位先生分别在《刘萨诃信仰解读一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和《民众佛教信仰的民间信仰化一以刘萨诃信仰为例》一文中对刘萨诃在民间信仰中的情况都做了深入和有意义的探讨。从另一个角度看,其“授记”能够预言“天下太平”、“国之兴替”这样的国家大事,这同一般的佛陀具有的能护佑功德主平安健康、治病送子及转世轮回的功能有所区别,其政治色彩比较强烈,而不是局限于民间。还有,刘萨诃在地狱冥游时受观音点化的经历,和魏晋之际地狱观念与观音信仰的流行有必然的联系。刘萨诃并非汉人,经观音点化,而后出家,而后成为高僧,而后成为利宾菩萨,而后成为刘师佛,这样一条逐级而上的完整的成佛路线,为修行者指明了方向,也赢得了他们的崇信。观音在这里又扮演了刘萨诃导师的角色,供奉刘萨诃实际上也就供奉了观音,这样好的事情之于佛徒和信众何乐而不为呢?出土自古浪县的圣历元年(698年)番禾瑞像,其碑身刻满了《心经》的经文(图十、图十一),
①《心经》是观音信仰的重要经典,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最后,番禾瑞像的称名。学术界至今都将其笼统地称为瑞像,而没有将真正的神格表达清楚,不论是早期提出后又被否定的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像,还是牛头山释迦瑞像、番禾瑞像等,都没有肯定其就是释迦牟尼或是其他的佛陀。众所周知,佛的诞生既需理论经典的支撑,又要通过造像来“藉像表真”,二者缺其一,就成了一条腿走路。番禾瑞像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一部成熟的经典来对它进行诠释,类似《道宣律师感通录》、《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稍有涉及,但都不足以说明。
六、小结
刘萨诃及其番禾瑞像的问题包含多个方面,这些问题都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笔者对刘萨诃西行河西一事的态度至今仍不能确信,因为其现有的资料不足以完全支持刘萨诃到过河西走廊,并做了这个也可能是河西佛教史上最为灵验的预言,遑论其“授记” 莫高窟、西游五天竺。刘萨诃的事迹自魏晋开始,历经隋唐五代宋各朝,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人们对刘萨诃的信奉反而有增无减,且不断加进了各种因素,因其预言而产生的番禾瑞像更是广受尊崇,其身上凝结了历史、民族、宗教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本身就非常值得探讨。实际上,目前大多数的讨论也集中在刘萨诃其人的“本生故事”和佛像发展史的讨论,还未能更加深入探讨其蕴含的哲理和要义。
刘萨诃是否到过番禾县“授记”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番禾瑞像在这里诞生了,不仅为当地僧俗所崇信,而且传播到了河西走廊以外的广大地区。有关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的问题仍需要不断探索,甚至可以汇集成一本专著。近来永昌县、炳灵寺、四川等地新发现了不少相关的造像、题记、雕塑等文物资料,可见其仍有新的研究材料出现,也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而继续深入地研究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相关问题,尤其对于中古时期历史、佛教、民族的交融发展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探讨的价值。
附注
①向达.中外交通小史[M].商务印书馆,1920(10).7
① 冯承钧《西力东渐记》1944 年版,第1 页。
②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24 ~ 125 页。
③ 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 年3 月版,第329 ~ 339 页。
④ 《西北历史资料》1985 年1 期,第1 ~ 10 页。
⑤ 《中国史研究》1979 年2 期,第142 ~ 152 页。
⑥ 《北京社会科学》1992 年1 期,第39 ~ 50 页。
⑦ 《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1 版, 耿升译,第1 ~ 4 ,58 ~ 73 ,140 ~ 149 ,284 ~ 294 页。
⑧ 《齐大国学季刊》新第1 卷第1 期。
①《天涯何处骊靬城:读书献疑》《读书》1994 年版, 第144 ~151页。
②《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 日。
①L.Carrington Goodrich, Homer Dubs(1892-1969) ,Th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9,No.4(Aug.,1970),pp.889-891.
①http://www.umass.edu/wsp/sinology/persons/duyvendak.html ②http://en.wikipedia.org/wiki/J.J.L._Duyvendak
③J.J.L.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in35B.C.,ToungPao, SecondSeries,Vol.35,Livr.1/3(1939),pp.211-215.
④这段记载出自《汉书》卷54,原文为:“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① J .J .L.Duyvendak, AComment on an Illustrated Battle-Account in35B.C.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35, Livr.1/3(1939), pp.211-213.② J .J .L.Duyvendak, AComment on an I llustrated Battle -Account in35B.C.,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35, Livr.1/3(1939), p.213.
①,J.J.L.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 in35B.C.,T' oungPao, Second Series,Vol.35, Livr.1/3(1939).pp.213-214
②.J.J.L.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Account in35B.C., T'oungPao, Second Series,Vol.35, Livr.1/3(1939).pp.214-215.
③J. J. L. Duyvendak, ACommentonanIllustratedBattle- Account in35 B.C. T' oungPao, econd Series,Vol. 35, Livr. 1/3 (1939). p.2 15 .
①1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5-66.
①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66-67.
②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2.
③许多人将重木城的“重”误拼为“zhong”,在翻回英文时误译为“heavy”,而根据原意,“重”应该是拼为“chong”,英文为“double”。
④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 oung Pao, SecondSeries, Vol.36, Livr.1(1940), pp.72-73.
①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3.
②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 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73-74.
① 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p.74-75.
②HomerH.Duds ,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T' 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5.
① HomerH.Dub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6.
② 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Chinese ,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322.
① 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p.322-323.
②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p.323-324.
① HomerH.Duds , An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p.324-325.
② HomerH.Duds , An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326.
①1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p.326-327.
② HomerH.Duds ,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Chinese , 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p.328-329.
① HomerH.Dud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p.329-330.
②HomerH.Dud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331.Homer
③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329.
④Homer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betweenRomansAndChinese,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p.329.
①Homer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 The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 No.3(1941), p.330.
②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 (Jan., 1943), p.13.
① 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3.
②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3-14.
①Homer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9.
①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ClassicalPhilology,Vol.38, No.1(Jan.,1943), p.16.
② 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6.
③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6-17.
① Homer 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 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 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7-18.
② Homer H.Duds , ARoman Influence upon 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 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18.
① HomerH.Duds , ARomanInfluence uponChinese Painting , ClassicalPhilology, Vol.38, No.1(Jan.,1943), pp.18-19.
①H.H.Dubs, ARomanCity inAncientChina , Greece and Rome, Vol.4, No.2(1957), p.139.
① 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0.②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p.140-142.
① 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andRome,Vol.4,No.2(1957), pp.142-143.
①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 No.2(1957), p.143.②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andRome,Vol.4,No.2(1957), pp.143-144.
①H.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Greece andRome,Vol.4, No.2(1957), p.146.
② 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6
①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p.147148.
②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8.
③HomerH.Dubs,ARomanCityinAncientChina.London:TheChinaSociety,1957, P.15.④HomerH.Dubs,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London:TheChinaSociety,1957, p.23.
① HomerH.Dubs, AMilitaryContact betweenChinese and Romans in36B.C., T'oung Pao, SecondSeries,Vol.36, Livr.1(1940), p.76.
②HomerH.Dubs, AnAncientMilitaryContact betweenRomans And Chinese , The American JournalofPhilology,Vol.62.No.3(1941), p.330.
③HomerH.Dubs, ARomanCityinAncientChina , Greece andRome,Vol.4,No.2(1957), p.146.
①然而,该信并没有地址,也没有找到关于菲利普活动的记载,其结果不得而知。
①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9页。
②古斯塔夫·奥波特和弗里德里希·赞克在19世纪晚期提出该观点,并不断地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例如Richard Hennig.Das Christentum im mittelalterlichen Asien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Saga vom Prester Johanness ,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 ⅩⅩIⅩ(1935), pp.234-252; and Terrae Incognitae, ⅡLeiden,1937, pp.361-376; L.N.Gumiev,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The Legend of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 Trans.By R.E.F.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③尽管该观点得到了亨利·裕尔和一些当代格鲁吉亚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已被弗里德里希·赞克推翻。
④ M.Bar-Ilan, Prester John: Fiction and History, History ofEuropean Ideas,20/1-3(1995), pp.291-298.
⑤David Morgan, Prester John and Mongols.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Trib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 pp.159-70.
① 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y Press,1999.
②吴梨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③ A.A.Vasiliev, Prester and Russia.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 pp.187-96.
④ Bernard Hamilton, Prester John and the Three Kings of Cologne.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pp..171-91.
⑤Charles E.Nowell, The Historical Prester John, Speculum, Vol.ⅩⅩⅤ Ⅲ, July1953, No.3,p.437.6
⑥M.Bar-Ilan, P rester John: Fiction and History' ,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20/1-3(1995), pp.291-298.David Wasserstein 认为,此信件的某些材料属于以色列十个迷失的部落,而约翰王的信件大约是在3个世纪后出现的。参见David Wasserstein,Eldad ha-Dani and Prester John.From 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pp..213-36.
⑦Charles F.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s.), Prester H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1996,pp..213-36.
⑧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了吴莉苇和龚缨晏教授研究成果的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①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这里的约翰王未必有其真人或拉丁名字名字是否有“Prester”之音,也许仅是后世借用说法而已。
② 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y Press.1999, p.11
③ Ibid., p.10
④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①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②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③即近印度(NearerIndia,又称“小印度”,指印度北部)、中印度、远印度(FurtherIndia,又称“大印度”,指印度南部)。
④转引龚缨晏:《约翰王:中世纪欧洲的幻象》,《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①JohnLarner,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YaleUniversyPress,1999,p.16.
②MatthewParis,EngilshHistory,Trans.J.A.Giles,London,1852,vol.1,pp.131-132;参见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一文中对《圣经》中歌各和玛各传说和“鞑靼人”来源的解释。
③腓特烈一世抱怨本来是对付穆斯林的十字军却用来进攻神圣罗马帝国,所以鼓励了鞑靼人来进攻分裂的基督教世界;而罗马教皇则怀疑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德皇引狼入室。
①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3~147,164~173页。
②同上,第166页。“此即吾人所称峨格(Gog)同马峨格(Magog)之地”。盖在此州中有二种人,先鞑靼人居住此地,汪格人是土著,木豁勒人则为鞑靼,所以鞑靼人常自称木豁勒,而不名曰鞑靼。”
③克烈部(Kerait)首领脱忽勒王罕(TogroulWang-Khan)
④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99页。
⑤这也是17、18世纪欧洲人难于接受“契丹”就是“中国”的宗教心理因素。
⑥Silverberg.The RealmofPrester John.Ohio University Press,1996, p.139.
①Matteo Salvadore , The Ethiopian Age of Exploration:Prester John's Discovery of Europe,13061458,JournalofWorld History,December,2010,p.599.
② Hans Werner Debrunner, Presence and Prestige,Africans in Europe:A History of Africans in Europe before1918,Basel,1979,p.24.转引自Matteo Salvadore,The Ethiopian Age of Exploration:Prester John'sDiscoveryofEurope.13061458,p.599.
③Jordanus,Mirabilia, chapter Ⅵ(2).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ster_John.
①Charles E.Nowell, The Historical Prester John, Speculum, Vol.ⅩⅩⅤ Ⅲ, July1953, No.3.
② Silverberg, The Realm of Prester John.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9.
③ Arrowsmith-Brown, J .H.(translator), Prutky's trave ls to Ethiopia and other countries .London: Hakluyt Society,1991.p.115.
④约翰王的故事激起了很多文学家的创作灵感。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威廉姆·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MuchAdoAboutNothing)其中的传奇国王就是以约翰王为原型;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小说家和政治家约翰·巴肯(JohnBuchan)的第十六部书《约翰王》中采用这个传奇题材;美国的惊奇漫画系列在一系列的《神奇四侠和雷神托尔》中具有约翰王的特征。查尔斯·威廉姆斯(CharlesWilliams)在1930年的小说《战争的天堂》(WarinHeaven)让约翰王成为圣杯的弥赛亚式的保护者;约翰王及其王国在乌姆博格图·伊库(UmbertoEco)于2000年发表的小说《波多里诺》(Baudolino)中名声大噪。
①Charles E.Nowell, TheHistoricalPresterJohn, Speculum,Vol.ⅩⅩⅤ Ⅲ, July1953, No.3.
②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45页。
①本文部分内容和观点最早于2011年8月“丝绸之路骊靬文化研讨会”期间公开,其后获得了部分新材料,修改后曾发表于《吕梁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①《隋书·高祖记》卷一。
①孙修身:《古凉州番禾县调查记》,《西北民族文丛》第三辑,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147~154页。
②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87、208页。
①《吕梁学院学报》刊登时在文中误将青龙山庙番禾瑞像与炳灵寺番禾瑞像顺序颠倒,借此勘误。
②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87、208页。
③据胡文和《安岳大足佛雕》161页所载图,笔者认为其标为49号龛的造像更似番禾瑞像,而165页所载64号龛却并非是番禾瑞像。因未亲至其处观察,不能确认,仅能据此书所载做初步的判断。
①图三、图十、图十一采自文静、魏文斌《唐代石雕刘萨诃瑞像初步研究》。
[1]卢秀文.刘萨诃研究综述[J].敦煌研究.1991(3):113~115.
[2]陈祚龙.刘萨河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J].华冈佛学学报.1973(3):33~56
[3]林幹.稽胡(山胡)略考[J].社会科学战线.1984(1).148~156.[4]杜斗城.河西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45.[5]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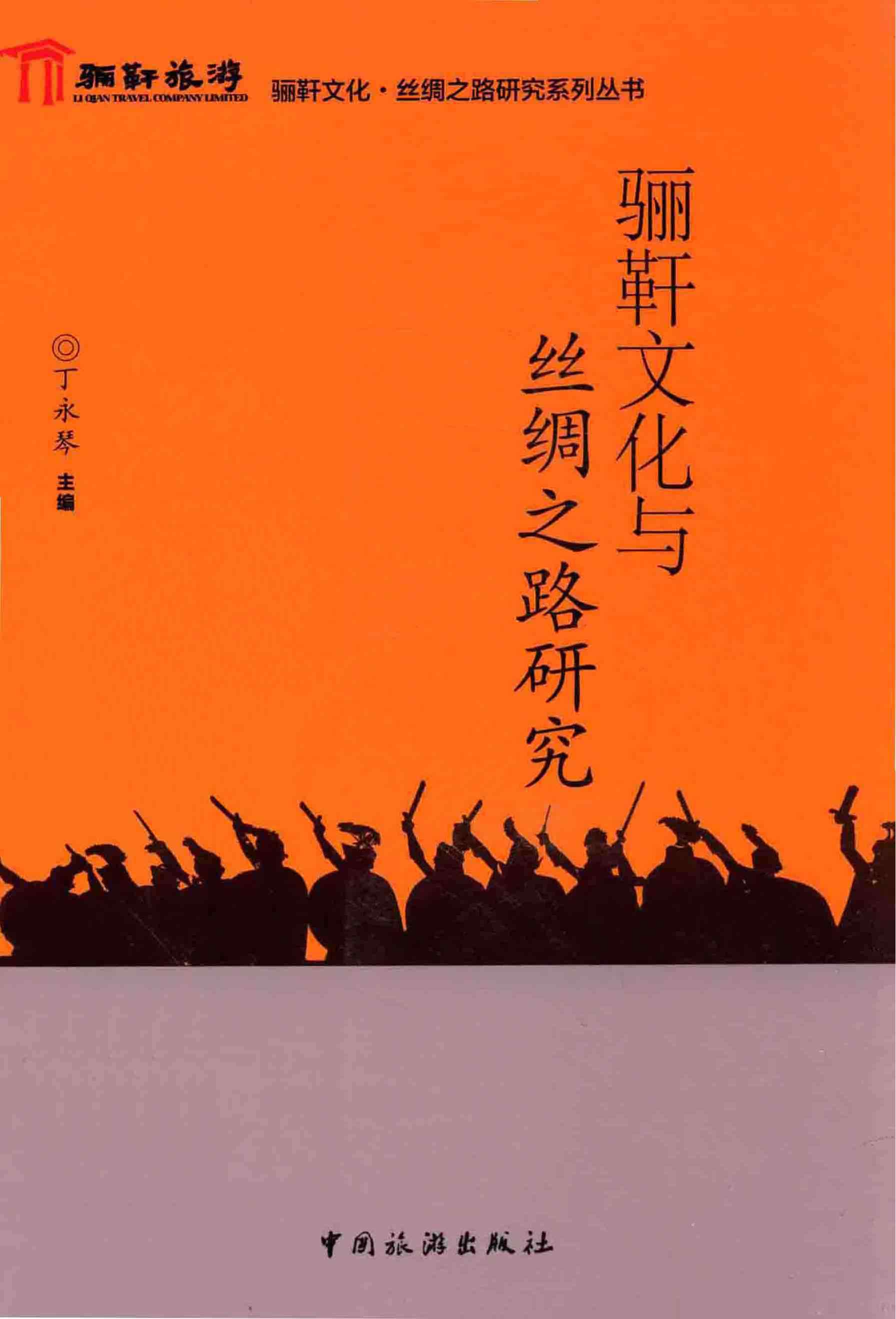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本书分骊靬文化与历史研究、骊靬文化旅游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研究、骊靬文学研究等四部分,收录了《古代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与战略定位》、《骊靬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展望》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