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足迹
| 内容出处: | 《永昌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216 |
| 颗粒名称: | 父亲的足迹 |
| 其他题名: | 记我的父亲红西路军老战士曾大明 |
| 分类号: | D235.57 |
| 页数: | 5 |
| 页码: | 247-25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作者的父亲红西路军老战士曾大明的人物事迹。 |
| 关键词: | 曾大明 红西路军 事迹 |
内容
1995年8月22日,严厉慈祥的老父亲永远离我而去,一名铁骨铮铮、艰苦朴素的红西路军老战士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按照父亲的嘱托,我将他身前的部分物品交县文化馆收藏,用以追忆红西路军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纪念他们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
我的父亲曾大明,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悦中乡天星村一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父亲跟随爷爷、大伯、大哥加入川陕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三十军九十师二六八团的一名小战士。1933年6月,按照木门会议的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后,父亲在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担任警卫排长,先后参加了营渠战役、嘉陵江战役,三过草地,两翻雪山,激战腊子口、大拉牌。1936年10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奉命西征,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征战河西走廊,历经靖远虎豹口、景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临泽梨园口、倪家营子、肃南石窝山等战役。
一 过雪山草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父亲跟随红四方面军一路北上。1936年3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向川康边境进发到达阿坝。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部队陷入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经过苦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川西道孚、甘孜一带。战士们饮冰雪、吃野菜、啃树皮、嚼草根,翻越了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
父亲一路随军北上,途经川西与甘肃交接处的毛儿盖、松潘、班佑地区以南纵横数百里的松潘大草地。茫茫无边,阴森、冰冷、浓雾笼罩着的草地,河沟交错,沼泽遍布、险象环生。在这广阔无垠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拔不出腿脚,直至全身沉入泥潭。红军将士踩着草墩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越是往草地中心走,越是艰险重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破旧衣衫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干。夜晚露宿时,更是奇冷难忍,战友们背靠背挤在一起取暖过夜。草地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粮食吃光了,只好沿路寻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皮带。但是父亲和战友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与风、雨、雪、霜、冰雹、严寒搏斗,与身体极限挑战,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高昂的革命斗志,每天坚持按计划的行程行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经甘肃岷县、临洮,与先期到达的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二 奉命西征激战永昌
1936年10月底,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三十军、五军、九军到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后因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渡河后随即与黄河对岸的马家军河防团交火。父亲所在的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一鼓作气打败黄河岸边的马家军,取得一条山大捷。战士们士气高昂,精神抖擞,转战河西走廊。刚到永登,还未站稳脚跟,马家军尾随而至,红九军与马家军喋血古浪,元气大伤。11月18日,红五军、三十军占领永昌县。
在进军永昌时,永昌东门外的战斗最为激烈。据父亲回忆,当时天上有蒋介石的飞机轰炸,地下有马家军的机枪扫射和骑兵的围追堵截。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组织机枪、步枪对空向敌机扫射。一次,几架敌机从西向东轰炸扫射,战士们对准敌机一阵猛烈射击,一架飞机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地拖着浓浓的黑烟向地下坠去。此举浇灭了蒋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将士的战斗士气。从此,敌人的飞机再也不敢低空飞行投弹。虽然将士们奋不顾身,英勇顽强,奋力反击,但是我军与数倍马敌作战,敌强我弱,终因气候寒冷,弹药缺乏,处于被动局面,在与敌马家军的激战中失利。父亲在永昌保卫战中左腿中弹受伤,简单包扎后仍然坚持继续作战。
三 浴血祁连山
1936年12月30日,红西路军进驻临泽沙河堡,直逼高台。当晚高台守敌投诚,红五军顺利攻占高台。父亲随三十军渡黑河后进驻临泽县倪家营子一带。之后,九军和红西路军军部直属单位也相继抵达倪家营子。不久,马家军集结所有部队与地方保安团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此时,红西路军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都处于劣势,马家军则以强大的优势兵力摆出一副将红西路军消灭殆尽的架势,红西路军将士以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在饥寒交迫中与敌血战40余昼夜,其中父亲所在的三十军担任防守的重任。
1937年3月7日,红西路军将士杀出一条血路,从倪家营突围,占据25公里外的三道柳沟,未等部队站稳脚跟,马家军便尾追而至。据父亲回忆,由于连日作战,战士们疲惫不堪,经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退守祁连山的小口子。马家军抄近路(从大口子进入)将红西路军合围,使红西路军完全陷入被动局面。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遂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战,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炸弹的爆炸声,喊杀声,狂风骤雨般的马蹄声响彻峡谷。我军将士顽强拼杀、浴血奋战,杀开一条血路,一部分将士向祁连山深处撤退。红西路军徒步行军一天,马家军的骑兵几小时就能追杀上来;红西路军徒步行军两天,马家军的骑兵半天就能追杀上来。战士们没有了枪和子弹,就用大刀跟马家军拼杀,往往四五个战士才能拼杀过一个马家军骑兵。在激烈的战斗中,将士们不分男女,不分伤势轻重,毫无畏惧,冲锋陷阵,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托砸;刀刃卷了,就用刀背砍;刀没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用嘴咬、用手抠,用自己的生命战斗到最后,流尽最后一滴血。
四 流落永昌城
3月14日,剩余的红西路军将士行至石窝山雪岭,军部领导决定: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军或东去寻找总部会合,再与敌周旋。
红西路军与马家军战斗失败后,父亲随同战友执行了军部首长的决定,为避免马家军的追杀,在祁连山中一路辗转,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曾经战斗过的永昌县,此时父亲因伤病复发,饥饿难耐,面临着生命危险。父亲拖着沉重的身子,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走到一个亮灯的住处,还未来得急敲门,就一头撞到门上晕死过去。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此人叫谢廷刚,祖籍四川,民国初年从四川流浪到永昌县,在县城内做了一个小炉匠,当时居住在东大街黄家坑沿。谢廷刚后来成为我的外公)听到响声,开门发现是一位受伤严重的红西路军战士,他不顾个人安危,把父亲背到屋里,用温水擦洗伤口,包扎好伤口后,再喂水喂饭,把父亲放在隐蔽处藏起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父亲的身体渐渐康复。那时,马家军到处抓捕迫害红西路军散落人员,风声紧的时候,父亲跑到大黄山上一边躲避,一边打柴背煤。吃树皮,沙柴籽,吃冰块,喝雪水,摘蘑菇,捕野兔,有时饿的撑不住时,甚至挖田鼠吃。
想起这段历史,父亲常常说:“也是我生与死的缘分吧。”当时,父亲脱离了部队,在永昌人生地不熟,无法立即找到组织,便决定暂时留在永昌,盼望有朝一日,待援军到来后杀个回马枪,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父亲所等的援军迟迟未到,父亲也一直未找到组织。据找到组织的战友们说,组织对流落的红西路军战士的答复是:一年收留,两年审查,三年回家。父亲已经过了收留和审查的年限。
不久,父亲便开始跟谢廷刚学习小炉匠的手艺,给周围的人们做油提子、铲子、烟筒、剪刀等物品,赚取一点零用钱。谢廷刚看到父亲为人忠厚、踏实吃苦、勤奋好学,是个好小伙,就将大女儿谢永芳嫁给父亲。与母亲结婚后,父亲便定居永昌,在永昌这片热土地上奉献自己的余生。
五 感念党的关怀
永昌解放后,县委、县政府为父亲颁发了《流落红军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父亲被诬称为“叛徒、逃兵”,受到了批斗,但父亲认为比起死去的战友,能幸运地活着,已经感到非常荣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父亲先后被安排在手工联社(铁器社)、铁工厂、永昌二轻局金属厂当工人。定居在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士们也受到党的政策鼓舞激励,相互联络、相互帮助,父亲常常帮助老战友们找县委、县政府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我们家便成了流落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友们交流、宣传红色文化的联络点之一。诸如李达义、刘永福、蒋绍才、龚少敏、侯秀英、黄玉贵、高开礼、熊九玲、熊明安、曾林模、陈世基、王世基和陈永红等30多名红西路军老战士,常来串亲访友、畅叙旧情。他们一同回忆那段艰辛历程,讲述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故事,高唱《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等红军歌曲,时而表情凝重、声音哽咽,时而激情澎湃、欢声笑语。1984年,跟其他定居在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士们一样,父亲领到了《西路红军老战士光荣证》,每月领取45元的生活费,医药费全额报销,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1983年9月,父亲当选为政协金昌市第一届委员;1987年3月,又被连选为政协金昌市第二届委员。
六 勤俭传家风
几十年前,父亲作战时胳膊受伤弯曲,拿取东西很不方便。左腿上,一直留着一颗与马家军作战时打进去的子弹头,经常会腿疼。1984年父亲离休,但父亲离而不休,一直在永昌影剧院门前摆摊设点做铁活,腿疼时父亲就会低着头,轻咬牙关,坐下休息一阵,不叫一声疼、不喊一声苦,风雨无阻地摆摊设点,做水桶、烟桶、油提子、花花子馒头的镊子等物。然而,父亲收取的费用很少,遇到经济困难的人索性不收费。父亲做的生活用品,走入了永昌的千家万户。
父亲从小严格教育我们,要是哪个孩子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就常常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严厉训斥:“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一次,我大哥将喝水的铁缸子说成尿罐,被父亲当场打了一个耳光。又有一次,我吃饭时,一根面条掉到地下,我没有捡,父亲看见后立即捡起来,用清水洗了洗自己吃了。父亲便拿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说:“当年我们战争时期的日子可苦了,吃草根、吃皮带、喝马尿、啃树皮,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么好的白面条浪费了多可惜啊!”我们家由于子女多,父亲工资低,生活条件差,父亲春夏秋三季一直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冬天穿毡靴。全家人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几年,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直到衣服破烂得无法缝补,母亲还得裁剪下来几块作为缝补其他衣服的料。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跟周围的邻居们相处融洽。要是谁家有个大小事情需要帮忙,他总会积极主动前去帮助。在学业上他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经常用四川家乡话对我们说:“龟儿子,你晓不晓得,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搞啥子去?”那时,我很小,非常喜欢听父亲浓浓的四川口音,感觉优美、温润、可亲。父母一生生育了我们5个儿女,我们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党组织的关怀下,现都在金昌这块热土地上努力工作,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作者系永昌县博物馆干部)
我的父亲曾大明,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悦中乡天星村一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父亲跟随爷爷、大伯、大哥加入川陕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三十军九十师二六八团的一名小战士。1933年6月,按照木门会议的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后,父亲在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担任警卫排长,先后参加了营渠战役、嘉陵江战役,三过草地,两翻雪山,激战腊子口、大拉牌。1936年10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奉命西征,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征战河西走廊,历经靖远虎豹口、景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临泽梨园口、倪家营子、肃南石窝山等战役。
一 过雪山草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父亲跟随红四方面军一路北上。1936年3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向川康边境进发到达阿坝。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部队陷入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经过苦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川西道孚、甘孜一带。战士们饮冰雪、吃野菜、啃树皮、嚼草根,翻越了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
父亲一路随军北上,途经川西与甘肃交接处的毛儿盖、松潘、班佑地区以南纵横数百里的松潘大草地。茫茫无边,阴森、冰冷、浓雾笼罩着的草地,河沟交错,沼泽遍布、险象环生。在这广阔无垠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拔不出腿脚,直至全身沉入泥潭。红军将士踩着草墩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越是往草地中心走,越是艰险重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破旧衣衫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干。夜晚露宿时,更是奇冷难忍,战友们背靠背挤在一起取暖过夜。草地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粮食吃光了,只好沿路寻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皮带。但是父亲和战友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与风、雨、雪、霜、冰雹、严寒搏斗,与身体极限挑战,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高昂的革命斗志,每天坚持按计划的行程行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经甘肃岷县、临洮,与先期到达的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二 奉命西征激战永昌
1936年10月底,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三十军、五军、九军到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后因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渡河后随即与黄河对岸的马家军河防团交火。父亲所在的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一鼓作气打败黄河岸边的马家军,取得一条山大捷。战士们士气高昂,精神抖擞,转战河西走廊。刚到永登,还未站稳脚跟,马家军尾随而至,红九军与马家军喋血古浪,元气大伤。11月18日,红五军、三十军占领永昌县。
在进军永昌时,永昌东门外的战斗最为激烈。据父亲回忆,当时天上有蒋介石的飞机轰炸,地下有马家军的机枪扫射和骑兵的围追堵截。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组织机枪、步枪对空向敌机扫射。一次,几架敌机从西向东轰炸扫射,战士们对准敌机一阵猛烈射击,一架飞机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地拖着浓浓的黑烟向地下坠去。此举浇灭了蒋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将士的战斗士气。从此,敌人的飞机再也不敢低空飞行投弹。虽然将士们奋不顾身,英勇顽强,奋力反击,但是我军与数倍马敌作战,敌强我弱,终因气候寒冷,弹药缺乏,处于被动局面,在与敌马家军的激战中失利。父亲在永昌保卫战中左腿中弹受伤,简单包扎后仍然坚持继续作战。
三 浴血祁连山
1936年12月30日,红西路军进驻临泽沙河堡,直逼高台。当晚高台守敌投诚,红五军顺利攻占高台。父亲随三十军渡黑河后进驻临泽县倪家营子一带。之后,九军和红西路军军部直属单位也相继抵达倪家营子。不久,马家军集结所有部队与地方保安团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此时,红西路军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都处于劣势,马家军则以强大的优势兵力摆出一副将红西路军消灭殆尽的架势,红西路军将士以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在饥寒交迫中与敌血战40余昼夜,其中父亲所在的三十军担任防守的重任。
1937年3月7日,红西路军将士杀出一条血路,从倪家营突围,占据25公里外的三道柳沟,未等部队站稳脚跟,马家军便尾追而至。据父亲回忆,由于连日作战,战士们疲惫不堪,经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退守祁连山的小口子。马家军抄近路(从大口子进入)将红西路军合围,使红西路军完全陷入被动局面。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遂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战,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炸弹的爆炸声,喊杀声,狂风骤雨般的马蹄声响彻峡谷。我军将士顽强拼杀、浴血奋战,杀开一条血路,一部分将士向祁连山深处撤退。红西路军徒步行军一天,马家军的骑兵几小时就能追杀上来;红西路军徒步行军两天,马家军的骑兵半天就能追杀上来。战士们没有了枪和子弹,就用大刀跟马家军拼杀,往往四五个战士才能拼杀过一个马家军骑兵。在激烈的战斗中,将士们不分男女,不分伤势轻重,毫无畏惧,冲锋陷阵,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托砸;刀刃卷了,就用刀背砍;刀没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用嘴咬、用手抠,用自己的生命战斗到最后,流尽最后一滴血。
四 流落永昌城
3月14日,剩余的红西路军将士行至石窝山雪岭,军部领导决定: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军或东去寻找总部会合,再与敌周旋。
红西路军与马家军战斗失败后,父亲随同战友执行了军部首长的决定,为避免马家军的追杀,在祁连山中一路辗转,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曾经战斗过的永昌县,此时父亲因伤病复发,饥饿难耐,面临着生命危险。父亲拖着沉重的身子,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走到一个亮灯的住处,还未来得急敲门,就一头撞到门上晕死过去。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此人叫谢廷刚,祖籍四川,民国初年从四川流浪到永昌县,在县城内做了一个小炉匠,当时居住在东大街黄家坑沿。谢廷刚后来成为我的外公)听到响声,开门发现是一位受伤严重的红西路军战士,他不顾个人安危,把父亲背到屋里,用温水擦洗伤口,包扎好伤口后,再喂水喂饭,把父亲放在隐蔽处藏起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父亲的身体渐渐康复。那时,马家军到处抓捕迫害红西路军散落人员,风声紧的时候,父亲跑到大黄山上一边躲避,一边打柴背煤。吃树皮,沙柴籽,吃冰块,喝雪水,摘蘑菇,捕野兔,有时饿的撑不住时,甚至挖田鼠吃。
想起这段历史,父亲常常说:“也是我生与死的缘分吧。”当时,父亲脱离了部队,在永昌人生地不熟,无法立即找到组织,便决定暂时留在永昌,盼望有朝一日,待援军到来后杀个回马枪,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父亲所等的援军迟迟未到,父亲也一直未找到组织。据找到组织的战友们说,组织对流落的红西路军战士的答复是:一年收留,两年审查,三年回家。父亲已经过了收留和审查的年限。
不久,父亲便开始跟谢廷刚学习小炉匠的手艺,给周围的人们做油提子、铲子、烟筒、剪刀等物品,赚取一点零用钱。谢廷刚看到父亲为人忠厚、踏实吃苦、勤奋好学,是个好小伙,就将大女儿谢永芳嫁给父亲。与母亲结婚后,父亲便定居永昌,在永昌这片热土地上奉献自己的余生。
五 感念党的关怀
永昌解放后,县委、县政府为父亲颁发了《流落红军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父亲被诬称为“叛徒、逃兵”,受到了批斗,但父亲认为比起死去的战友,能幸运地活着,已经感到非常荣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父亲先后被安排在手工联社(铁器社)、铁工厂、永昌二轻局金属厂当工人。定居在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士们也受到党的政策鼓舞激励,相互联络、相互帮助,父亲常常帮助老战友们找县委、县政府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我们家便成了流落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友们交流、宣传红色文化的联络点之一。诸如李达义、刘永福、蒋绍才、龚少敏、侯秀英、黄玉贵、高开礼、熊九玲、熊明安、曾林模、陈世基、王世基和陈永红等30多名红西路军老战士,常来串亲访友、畅叙旧情。他们一同回忆那段艰辛历程,讲述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故事,高唱《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等红军歌曲,时而表情凝重、声音哽咽,时而激情澎湃、欢声笑语。1984年,跟其他定居在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士们一样,父亲领到了《西路红军老战士光荣证》,每月领取45元的生活费,医药费全额报销,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1983年9月,父亲当选为政协金昌市第一届委员;1987年3月,又被连选为政协金昌市第二届委员。
六 勤俭传家风
几十年前,父亲作战时胳膊受伤弯曲,拿取东西很不方便。左腿上,一直留着一颗与马家军作战时打进去的子弹头,经常会腿疼。1984年父亲离休,但父亲离而不休,一直在永昌影剧院门前摆摊设点做铁活,腿疼时父亲就会低着头,轻咬牙关,坐下休息一阵,不叫一声疼、不喊一声苦,风雨无阻地摆摊设点,做水桶、烟桶、油提子、花花子馒头的镊子等物。然而,父亲收取的费用很少,遇到经济困难的人索性不收费。父亲做的生活用品,走入了永昌的千家万户。
父亲从小严格教育我们,要是哪个孩子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就常常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严厉训斥:“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一次,我大哥将喝水的铁缸子说成尿罐,被父亲当场打了一个耳光。又有一次,我吃饭时,一根面条掉到地下,我没有捡,父亲看见后立即捡起来,用清水洗了洗自己吃了。父亲便拿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说:“当年我们战争时期的日子可苦了,吃草根、吃皮带、喝马尿、啃树皮,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么好的白面条浪费了多可惜啊!”我们家由于子女多,父亲工资低,生活条件差,父亲春夏秋三季一直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冬天穿毡靴。全家人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几年,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直到衣服破烂得无法缝补,母亲还得裁剪下来几块作为缝补其他衣服的料。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跟周围的邻居们相处融洽。要是谁家有个大小事情需要帮忙,他总会积极主动前去帮助。在学业上他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经常用四川家乡话对我们说:“龟儿子,你晓不晓得,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搞啥子去?”那时,我很小,非常喜欢听父亲浓浓的四川口音,感觉优美、温润、可亲。父母一生生育了我们5个儿女,我们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党组织的关怀下,现都在金昌这块热土地上努力工作,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作者系永昌县博物馆干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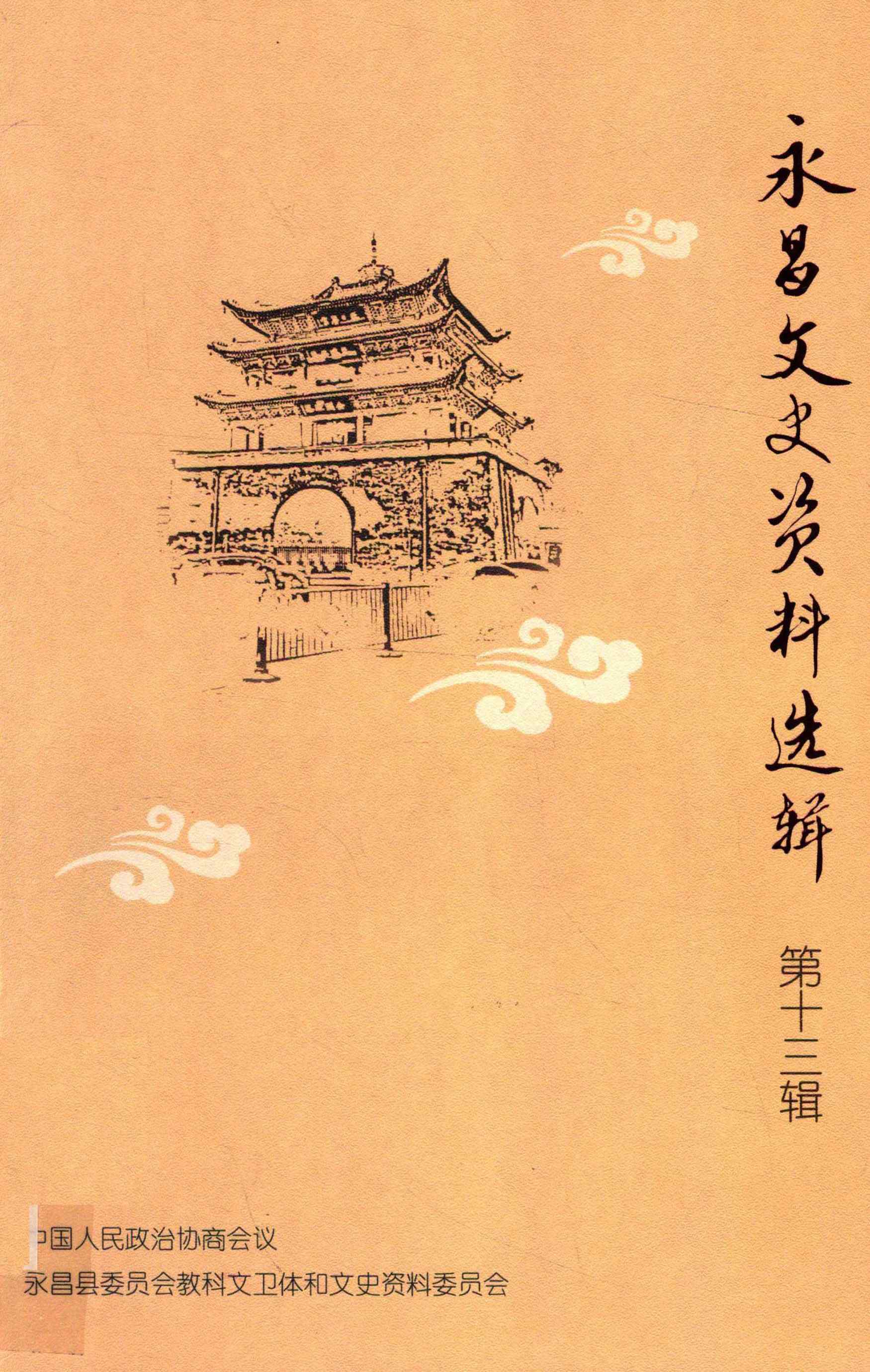
《永昌文史资料选辑》
本书共分历史文化篇、考古文化篇、文学文艺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篇、党史与西路军专题五个部分,内容总体布局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辑录了永昌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文物、文艺作品乃至亲历者的口述史,图文并茂,力求真实而生动地再现永昌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也必将是一部爱国主义和优秀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阅读
相关人物
曾家文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曾大明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