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王考
| 内容出处: | 《永昌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1173 |
| 颗粒名称: | 永昌王考 |
| 分类号: | K297.57 |
| 页数: | 15 |
| 页码: | 033-04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谁是永昌王?关键涉及到二人:一是铁木真之孙、窝阔台之子阔端;一是窝阔台之孙、阔端三子只必帖木儿。参照《元史》与相关史料,就此问题作一考辩。其中包括了阔端是窝阔台汗封授的西凉王、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永昌王等。 |
| 关键词: | 永昌王考 历史文化 永昌县 |
内容
谁是永昌王?关键涉及到二人:一是铁木真之孙、窝阔台之子阔端;一是窝阔台之孙、阔端三子只必帖木儿。参照《元史》与相关史料,就此问题作一考辩。
一 阔端是窝阔台汗封授的西凉王
《元朝秘史》《元史·本纪》记载: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草原上分裂的局面。太祖元年(公元1206),蒙古各部实现统一,铁木真作为各部共主,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自大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古汗国。
蒙古建国后,为了加强和巩固蒙古汗国的内部统一,成吉思汗着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权组织机构。
首先,设置了蒙古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札鲁忽赤”,蒙古语意即“大断事官”,相当于“丞相”的职务,负责处理民户分配和司法诉讼,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委任其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
其次,继续完善十进制军政管理体制,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全部蒙古人以千户为单位加以整编,打破了原来的氏族或部落组织形式。
同时,为了确保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将护卫军扩充至上万人,包括精选出来的一千名宿卫、八千名散班和一千名箭筒士。护卫军负责保护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他的幼子拖雷负责护卫军的组织、指挥及兵马的装备。另外委任忽必来为最高军事长官,称作“军事那颜”。
土地分封制也是维护蒙古统治集团的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因此,建国后就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属于大汗。
成吉思汗本人及后妃,直接控制着怯绿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又因为蒙古人在帐幕里居住,所以建立了“斡耳朵”制,“斡耳朵”蒙古语意为宫帐。成吉思汗设置了四个斡耳朵,将皇后和妃子们分别安排在其中。大汗的私人财富,也分属四个斡耳朵;大汗死后,其财富由四个斡耳朵分别继承。这一制度为历代蒙古大汗所承袭。
随后,成吉思汗以家族中血缘亲疏为标准,同时参考功劳的大小对土地进行了分配。在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为“黄金家族”,他的正后孛儿帖所生的四个儿子又被誉为“汗国宫廷的四根栋梁”。他任命长子术赤掌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管法律,三子窝阔台治理朝政,四子拖雷负责护卫。除了拥有至高的权力地位之外,王子们同样拥有各自的“兀鲁思”,意即“国中国”。在各自的封地内,诸王们拥有自主权,他们对所得的“份额”,有向子孙后代进行再分配的权力,王位也可以世袭。
成吉思汗的亲族弟兄们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铁木哥和别里古台的封地在其大“兀鲁思”东部,所以这些领主又被称为“东道诸王”。至此,蒙古汗国的统治体制、制度及法令逐渐完善起来。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一切,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他要用武力去征服周边的领域。
从此,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又长期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用兵,是对夏、对辽、对金、对宋,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对西方的用兵,则从中国境内远到中亚、欧洲。太祖四年(1209),蒙古军进攻西夏,西夏战败,纳女请和。畏兀儿人慑于蒙古军的威势,于五年遣使归顺。十三年,蒙古军灭掉了西辽。从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西征。蒙古侵略军首先灭掉了花刺子模,占领了中亚、伊朗和阿富汗的大片领土。接着,又大败俄罗斯联军于乌克兰境内的迦勒迦河。七年后回军东归蒙古。在西征回军途中,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派军随从西征及不送质子为借口,于太祖二十一年(1226)大举进攻西夏。蒙古兵分两路,成吉思汗亲率一路十万大军由漠北南下,越过黑水、贺兰山,直取武威,歼灭西夏军主力。另一路从西域出发,经哈密地区东进,攻取敦煌、酒泉、张掖。二十二年(1227)八月,在强大的蒙古铁骑攻击下,西夏政权灭亡。这一年二月,术赤病殁在咸海北方草原的封地深处,比他父亲先死六个月,时年47岁。四月,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八月病逝于秦州清水县西江驻地大帐中,在位22年,享年66岁。在汗位虚悬的两年中,幼子拖雷监国摄政。按照蒙古习俗,幼子又曰“斡惕赤斤”(灶主),可继承父母的财产而守家帐。所以,拖雷号称“也可那颜”(大官人),得以掌握成吉思汗的宫帐、牧地、怯薛护卫和大部分千户。拖雷有十一子。王妃唆鲁和帖尼所生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留名于史籍。
根据蒙古大汗的继承制度,大汗生前示意或指定某子孙继位,死后再召集亲王驸马、将相大臣参加库里尔台(部落议事制度)大会,共同推举新大汗。在蒙古语中,“库里尔台”是“盛大聚会”的意思。成吉思汗病逝两年后的太宗元年(1229)秋,蒙古诸王诸将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了库里尔台选汗大会。大会争议40日而不能决定人选。汗廷内恪守旧制的拖雷麾下的宿将老臣们主张继立统军最多的拖雷,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此时术赤已死,在二兄察合台的鼎力扶持下,经过耶律楚材和速不台等的劝说,大会才达成协议,承认成吉思汗的遗愿,推选窝阔台为大汗。
太宗十三年(1241)十一月,窝阔台酒后得病,十二月崩于行殿,终年56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由其遗孀长妻或幼子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由于窝阔台的正宫孛刺合真皇后无子,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也死去。身为诸子之母的脱列哥那——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摄政五年(1242-1246)。乃马真氏称制元年,察合台病殁封地。到此时成吉思汗的诸子已经相继谢世,孙辈叱咤风云的时刻即将来临。
定宗元年(1246)七月,蒙古汗廷在和林举行库里尔台选汗大会。金顶大帐内争论激烈。会上,有人提出失烈门(阔出长子)曾是窝阔台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应当即位。阔端以成吉思汗曾一度提到要他做汗位继承人为由,也站出来争位(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记载)。但是,在称制者六皇后乃马真氏的主持操纵下,大会以失烈门尚处幼年,阔端体弱多病为由,否定了他们。在乃马真氏的提议坚持下,宗王贵族们选定窝阔台长子贵由为汗位继承人。八月即位,是为定宗。贵由继立,在位三年,而猝然死去。时年43岁。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热衷追逐权力,积极介入蒙古汗廷残酷的争权斗争,于1249年称制,临朝视事三年,不得令终。
窝阔台有七个儿子,即贵由、阔端、阔出、哈刺察儿、合失、合丹、灭里。前五子的生母是六皇后乃马真氏,后二子的生母是业里讫纳妃子。
窝阔台即位后,把自己的几个儿子相继封王。未登汗位以前,他的草原领地在叶迷立和霍博一带。即位后,以上封地授予长子贵由。又将中原西夏故地封授给次子阔端。其他子孙驻牧于漠北窝阔台汗四季行宫附近。成吉思汗给诸子封授千户军队时,三子窝阔台受封五千户,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六十多个千户的军队和部众。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妃子继续掌管他麾下的军队、部众和封地,并抚育四个儿子。此时,窝阔台汗未和宗亲商议,擅自将拖雷系所辖的逊都思部二千户和雪你惕部一千户拨给皇子阔端,窝阔台系宗王拥有的蒙古千户数总计应在八千户以上。
窝阔台执政时期采取的多方面政策措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汗国的政权建设,也为提高大汗的地位,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合《元史·食货志》丙申(1236)年的具体记载,我们得到明晰的数据:平阳府41000多户分配给术赤系;太原府47000多户划归察合台系;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又分得大名府的68000多户,次子阔端又分得东平府的48000多户;真定路的80000多户分给拖雷系;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忽兰皇后所生)分得河间府的45000多户……
阔端,《元史》无传。称为“阔端太子”,即“阔端皇子”。又译作扩端、阔丹、库腾等。凉州地方志碑铭中多称也燀火端王、果诞王等。这是由于音译使然。阔端有五子:灭吉里歹、蒙哥都、只必帖木儿、帖必烈、曲列鲁。
窝阔台继位后,就派阔端镇抚秦、蜀、吐蕃等地,“开府西凉”,称西凉王。他逐步招抚了四川地区的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并任命许多吐蕃首领为边州长官。
太宗七年(1235),窝阔台举行了忽里尔台大会,决定了“长子出征”东欧和阔端、阔出等进兵宋境的军国大事。阴历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大举南侵。东路军由宗王口温不花率领,进攻江淮地区;中路军由阔出率领,进攻汉水及长江流域;西路军由阔端率领,进攻四川。
东路军于阴历六月征伐江淮,到十一月接连攻陷淮西的光州、蕲州、舒州。进攻真州时,被南宋的知州邱岳置炮设伏击败,收兵北还。
中路军于阴历七月初进兵唐州,开始大规模入侵襄汉地区。太宗八年,蒙古军占领襄阳。不久,因为蒙古主将阔出战死,襄阳又被宋军收复。
战事初起,西路军迅速出凤州取沔州,但是,在蜀北咽喉青野原被宋将曹友闻击退。太宗八年(1236),蒙军调集50万兵力,再次大举进攻四川,宋军被迫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阴历九月,蒙军破阳平关,宋将曹友闻战死。随后,蒙古军长驱入蜀,一月之间,连续占领成都、利州、潼州三路的绝大部分州郡,兵民惨遭焚掠屠杀。当年冬,蒙军主力撤出四川,部分军队进抵长江北岸后退兵。九年,阔端引兵北上,驻扎凉州,经营吐蕃。
《元史·赵阿哥潘传》云:“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藏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皇子阔端之镇西土也,承制以阿哥昌为迭州安抚使。”《高智耀传》又云:“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国。……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復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欲奏官之,不就。”《孟德传》亦云:“太宗即位之八年,诸王阔端命德为元帅,佩金符,领济南军攻宋徐州、光州,降其众而有其地。”从这些记载看出:阔端在皇族中的特殊地位和镇抚河西时的握权之重。
窝阔台执政十三年后病死。壬寅(1242)年春,乃马真后临朝摄政。皇子阔端依旧“开府凉州,承制得专封拜”(《新元史》),继续镇守西凉。
明崇祯十六年(164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成《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此书详细记载了从西藏有史以来直至顾实汗之间,所有历代王朝事记和王嗣传统。书中记载:“汗(成吉思汗)有子嗣多人,一子名阿阔台。台有二子名贵由和阔端。阔端皇子曾遣多达那布西征入藏,其攻战之术,虽大自天亦生畏惧,而以之加诸藏地,故金藏莫不为之慑服……并遣使回到王庭。称言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若以今生圆满福报而论,此赡部洲如成吉思汗之所受享,再无过者。倘求后世有利,则应迎致佛教大师,宜讲解脱和一切种智之道,最关紧要。未久,使臣返藏,携有迎请萨迦班智达之函扎,及下达萨迦法主之敕令。甲门来到萨迦,宣王旨意。”“继后,师应霍尔汗王之命,前往汉霍等地,故能于此殊方绝域,以不可计量之身、语、意三密事业,光显如来之圣教也。适汗王为地祗龙神所祟,师作至上无畏之布施,使其解脱疾苦。……最后,大师庄严之化身,则收入于此幻化寺中而圆寂也。”这些记述,与史实基本相符。“赴霍尔汗王之命”即“赴西凉阔端大王之命”。
太宗十一年(1239)秋,蒙古大将多达那布等奉阔端之命领兵进入前藏。在前往藏区的途中遇到藏族民众和武装僧人的反抗,双方发生冲突,各有伤亡。蒙古军杀害了几百名僧人,并烧毁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此后,多达那布在藏区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次年,他返回凉州,将了解到的西藏社会状况、地方僧俗势力及各教派的情况,向阔端作了汇报,并呈《请求迎谁为宜的详禀》,建议迎请萨班作为代表,来凉州磋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阔端采纳了多达那布的建议。
乃马真后三年(1244)八月,阔端再次派遣多达那布入藏。这次多达那布是以金字使者的身份前往,以多尔斯衮为正使组成使团。他们带着阔端的《邀请诏书》和许多礼物来到西藏(见《萨迦世系史》)。
为了雪域民众的安危和长远利益,萨班接受了阔端的邀请。于乃马真后三年底,不顾63岁的高龄,携其侄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以及精通五明的一些学者,从后藏萨迦起程,经过两年的艰辛跋涉,至五年(1246)八月抵达凉州。但此时的阔端远在蒙古高原的和林参加推举贵由继任大汗的会议,萨班未能见到阔端。直到定宗二年(1247)年初,阔端从和林返回,他们终于在凉州会面。
这一年,萨班与阔端分别作为西藏僧俗各界代表和蒙古汗国代表,就西藏归顺问题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史称“凉州会盟”。经双方磋商,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由萨班给卫藏各僧俗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一起归顺,这就是著名的《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信中详述了归顺与否对于佛法和世俗权力的利害关系,以及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派官设治、交纳贡赋、萨迦与其他官员僧俗共管西藏事务等意见,奠定了至元十六年(1279)以后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行政管理的基础,萨迦派由此也取得了卫藏地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地位。
宪宗元年(1251)阴历六月,在蒙古本土三河源头的阔帖兀阿兰之地召开了忽里尔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术赤系、拖雷系诸王、东道诸王,以及一部分察合台系诸王和窝阔台的六子合丹、七子灭里、孙子蒙哥都。虽然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多数后裔不参加会议进行抵制,但大会仍然如期举行。蒙哥得到术赤之子拔都、别儿哥相助,登上了蒙古汗国第四任大汗的宝座,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家族。成吉思汗的子孙间开始了内讧和杀戮,蒙古汗国内部出现了裂痕。《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即位伊始,蒙哥汗就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负责人选都重新作了安排。特意命同母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政大权,治理蒙古、汉地民户,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区等都属忽必烈管辖。宪宗二年八月,蒙哥汗“驻跸和林。分迁诸王於各所:合丹於别石八里地,蔑里於叶儿的石河,海都於海押立地,别儿哥於曲儿只地,脱脱於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於没脱赤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於军营。”合丹、灭里,皆窝阔台之子。海都,合失子;脱脱,哈刺察儿子;蒙哥都,阔端子;皆窝阔台之孙。乞里吉忽帖尼,窝阔台三皇后。失烈门,阔出子,窝阔台孙,后被投水溺死。也速即也速蒙哥,察合台子。孛里(不里),察合台孙,实际被杀。和只(忽察)、纳忽(脑忽),贵由子,窝阔台孙。也孙脱,察合台孙。别儿哥,蒙哥即位时的拥立者,术赤次子。蒙哥汗毫不留情地追究、肖弱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后王等反对其即位的势力,严厉惩罚企图发动政变的堂兄弟们。前摄政皇后海迷失被审后缝入一个口袋投水淹死。失烈门的生母合答失赤,贵由汗的亲信、镇守波斯军队最高统帅野只吉带以及失烈门、脑忽和忽秃黑(哈刺察儿子)三王的亲信七十多人,也因参与夺权密谋而被处死。窝阔台诸后妃的家赀也被分赐给拖雷系亲王。
随后,窝阔台汗国被划分为六个小王国,使窝阔台家族不能形成威胁汗位的力量。分别由合丹、灭里、脱脱、海都等治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他的旧部,另委亲王统带。只有阔端诸子仍保留封地和军队。但剥夺了阔端独治吐蕃的权力。不久,蒙哥汗下令处死了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也速蒙哥,由哈刺旭烈兀接任察合台汗国的可汗。
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记载:当窝阔台合罕家族的成员谋叛蒙哥合罕时,他们的军队都被夺走了,除阔端诸子的军队以外,全部被分配掉了。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蒙哥汗是将窝阔台系宗王的千户军队由原先的八千户削减至三千户。阔端诸子的三千户军队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所属的逊都思部等军队与拖雷家族关系密切,致使阔端诸子对蒙哥汗等一直十分友好。
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记载:1252年8月,蒙哥到达和林,在那里,他完全制服了他的敌人,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追究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罪状,在这以前,她一直是被宽恕的……窝阔台系只有两支,例外地没有遭到迫害,这就是阔端与合丹。合丹对于‘密谋’丝毫没有参与,他和忽必烈关系很密切,将来成为忽必烈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另外,阔端的儿子们曾主动地及时到达蒙哥那里向他致以应尽的敬礼。
《多桑蒙古史》亦载:“……谪窝阔台诸子于各地,夺其父所遗之部兵,以畀翊戴无贰心之诸王。惟合丹灭里二王及阔端诸王早诚心归命,不仅未夺其兵,且各以窝阔台之斡耳朵一所,后妃一人赐之。蒙哥究违命诸臣,遣使至各地,凡附窝阔台系者,皆逮治之。”
经过汗位争夺战,窝阔台和察合台系诸王势力倍受打击,而蒙哥和拔都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因此,蒙哥即位后,蒙古汗国主要掌控在拖雷系和术赤系诸王的手中。窝阔台系这一支血脉就衰落了,仅保留了一块“窝阔台后王封地”。拉施特说:“自此不幸时代以后,蒙古遂受内乱之害,诸王似忘成吉思汗和睦保国之遗训。”
至此,“黄金家族”的内部斗争得以平息,蒙哥通过对异己势力的严厉镇压,巩固了汗位,开始着手处理国事。
宪宗元年,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享年70岁。他的16岁的侄子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五祖。根据阔端的意旨,在凉州幻化寺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灵塔,以安葬萨班的灵骨。
就在同一年末,阔端也病殁于凉州。据清初蒙古族史家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记载:阔端于蒙哥元年(1251)去世,时年46岁。从《元史》中也可看出,阔端的行事重点在窝阔台执政和乃马真氏称制时期,蒙哥即位后渐趋消失。因此判断:《蒙古源流》的说法是可信的。
阔端病死后,蒙哥汗诏命阔端长子蒙哥都承袭西凉王王位,镇守河西。自此以后,西凉王受忽必烈亲王节制。蒙哥都的事迹,曾在《元朝秘史·长子出征》一节的叙述中出现。宪宗八年(1258),蒙哥汗征宋攻蜀的战争中,蒙哥都随征于西路军。十一月,“诸王蒙哥都攻礼义山不克”;九年,“诸王蒙哥都復攻渠州礼义山”。
明宣德五年(1430),由国师锁南监参募集资金,对幻化寺进行了重修。《重修凉州百塔志》碑文中云:“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百塔,不知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也燀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撤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焚,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曰:庄严。……”碑文中的人名“也燀火端王”即阔端,“撤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均为同一人名的异译。《中华大字典》释文为:“燀,党旱切,音亶(胆),旱韵。”蒙古语“亦(也)赫(燀)”是汉语“大”的意思。凉州“也燀火端王”就是“凉州大阔端王”,即凉州阔端大王。
清康熙年间,再次重修幻化寺,并立碑记载。《重修白塔碑记》中云:“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翻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果诞王”即阔端王;“板只达”即萨迦班智达;“乌斯藏”即卫藏,指今天的西藏。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阔端不是永昌王,而是窝阔台汗封授的以地制名的西凉王、凉州大王。
二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永昌王宪宗元年末,阔端在凉州病故。长子蒙哥都承袭西凉王,镇守其父河西封地。二年八月,蒙哥汗下令分迁诸王到各驻所时,将凉州大王蒙哥都迁徙至“扩端所居地之西”,那里有窝阔台的世袭领地。阔端的河西封地又命其三子只必帖木儿镇守。在祁连山的南麓北麓,直至焉支山下的广阔草原上设有蒙古汗国的皇家牧场,为汗廷供给了无数的优良战马。阔端驻牧设帐,驻夏行宫在永昌皇城滩,驻冬之所在西凉府。因此,只必帖木儿的镇所设在永昌。三年(1253),蒙哥汗以中州封宗亲,赐封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
宪宗六年(1256)春,蒙哥汗在蒙古中部举行忽里尔台会议,诸王移相哥、驸马也速儿等提议尽快征伐南宋。蒙哥汗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对这次亲征南宋,蒙哥汗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幼弟阿里不哥和皇子玉龙答失留守和林,主持蒙古汗国庶政,管理漠北千户军队和诸斡耳朵宫帐。进攻南宋的军队分为东、西、南三路。东路军由诸王塔察儿率领,攻略荆襄。因进军不利,改派忽必烈统领,侵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西路军随蒙哥汗出发,进攻川蜀。西凉袭王蒙哥都随征。南路军是兀良合台所率的云南蒙古军和蛮焚军一万三千,进攻路线是经广西、贵州趋潭州(今长沙)。三路军队总数10余万,试图对南宋实施三面围攻,这显然是一次旨在灭亡南宋的战略性大进军。
蒙哥汗于八年(1258)阴历十月取道汉中抵达利州。在巩昌总帅汪德臣的协助下,蒙哥所统军队渡嘉陵江和白水江,攻取地势险要的苦竹隘。又沿嘉陵江东下,拔南宋潼川府治长宁山城,招降阆州大获城及运山、青居、大良等城。年底,蒙古军顺嘉陵江南下,欲进攻南宋在四川的大本营重庆。没料到在重庆北的钓鱼山遇到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
九年阴历二月,蒙哥汗在扫清外围之后,亲自督促蒙古军和汉军对钓鱼城展开强攻。但连续攻战五个月,损兵折将,未能破城。连为蒙哥充当御前先锋的汪德臣,也在攻城时负伤“感疾”而亡。七月,蜀川一带暑热难忍,军中瘟疫流行。蒙古军只好暂时停止对钓鱼城的进攻,转而南攻重庆。而蒙哥竟在转移营地途中,病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时年52岁,在位9年。蒙古军丧失主帅,随征军除汪氏和纽磷的军队留下外,其余都随蒙哥的儿子阿速台从重庆府、合州等地撤兵北返。
蒙哥汗猝死以后,蒙古人停下了西征的脚步,也终止了南侵宋朝的行动。然而,在周边世界得以喘息之时,蒙古的权贵们却又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内斗。
蒙哥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这就为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留下了空间。
统领漠南中原事务之后,忽必烈打破蒙古部族的传统统治政策,起用儒者,尝试“以汉法治汉地”。宪宗六年春,忽必烈决定改革在桓州、抚州间设帐而居的状况,下令在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修筑新城,营建宫室房舍,三年后建成,定名为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作为王府常驻之所。开平府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地区之间,地势冲要,既便于与和林的大汗相联系,也有利于控制中原。开平的兴建,显示忽必烈以儒臣治理汉地的统治方式已初见成效。
中统元年(1260)阴历三月,忽必烈抵达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在诸王的建议下,忽必烈在开平自行召开了忽里尔台大会。
在塔察儿的提名和推举下,忽必烈登上了大宝之位,年46岁。四月,颁即位诏于天下,宣称:“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
四月,阿里不哥在哈刺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也召开了选汗的忽里尔台会议。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多数是成吉思汗直系的西道各支宗王。在这一部分蒙古汗廷宗王和权臣们的拥立下,阿里不哥也称汗即位。
这样,蒙古汗国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分别是拖雷的两个儿子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二人曾经派出许多急使,进行谈判和交涉。但因双方互不相让,未能达成协议,只能诉诸武力。
关陇之战的序幕是在中统元年(1260)五月拉开的。
蒙哥汗亲征川蜀时,曾留浑都海部4万骑兵屯戍六盘山。他攻打合州殁于钓鱼山之后,随他进攻南宋的蒙古军和汉军大部分由他的儿子阿速台统领,向北移动。阿里不哥即命部将阿蓝答儿为阿速台所领这支军队的主帅。浑都海率所部军队离开六盘山,西渡黄河,直趋甘州。阿蓝答儿自和林率军南下接应,遂与浑都海会合。阿蓝答儿、浑都海遂合军东攻西凉府只必帖木儿王领地。
八春、汪良臣二军奉命西去御敌,与浑都海军相持两月,未见分晓。九月,合丹大王及诸王哈必赤、阿曷马等率骑兵参战,会同八春、汪良臣部与阿蓝答儿、浑都海在甘州东删丹附近的耀碑谷展开决战。
忽必烈委任西道诸王合丹为全军统帅,统一号令指挥,分三路以迎敌。合丹列阵于北,八春列阵于南,汪良臣列阵于中。时值大风吹沙,天色阴晦,汪良臣命令军士下马,用短兵器突然袭击敌军左翼,绕出阵后,又击溃右翼。八春直捣敌军前部,合丹指挥精锐骑兵截断敌军归路,大败敌军,斩阿蓝答儿和浑都海,杀伤俘虏不计其数。只有部分残军逃回到吉儿吉思——阿里不哥的封地。
为了震慑敌人,稳定局势,京兆等路宜抚使廉希宪命令将阿蓝答儿、浑都海枭首于京兆(西安)示众三日。关陇之战遂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西土悉平。
随后,忽必烈立即转入主战场,就以成吉思汗的嫡孙和拖雷诸子的兄长身份乘胜去逐鹿蒙古本土漠北,统军进攻和林,亲征昔木土,大获全胜。战胜了阿里不哥,夺回了漠北的控制权,证明自己是合乎蒙古传统的大汗。
中统五年(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不得不南下归降忽必烈。第二年秋天,阿里不哥病死。
为了庆祝阿里不哥的归降和蒙古汗国的重新统一,是年八月,忽必烈特意将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以示否往泰来和鼎新革故之义。
至元元年(1264)八月,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废除“大蒙古”国号,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之意)。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灭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经过以上历史脉络的梳理,具体问题渐趋显现,为我们解读史料铺垫了基础。现将《元史》中有关资料列录如下:
《按竺迩传》:“中统元年,世祖即位,亲王有异谋者,其将阿蓝答儿、浑都海图据关陇。时按竺迩以老,委军於其子。帝遣宗王合丹、哈必赤、阿曷马西讨。按竺迩曰:‘今内难方殷,浸乱关陇,岂臣子安卧之时耶?吾虽老,尚能破贼。’遂引兵出删丹之耀碑谷,从阿曷马,与之合战。会大风,昼晦,战至晡,大败之,斩馘无算。按竺迩与总帅汪良臣获阿蓝答儿、浑都海等。捷闻,帝锡玺书褒美,赐弓矢锦衣。”
《廉希宪传》:“诏以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浑都海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阿蓝答儿復自和林提兵与之合,分结陇、蜀诸将,又使纽磷兄宿敦为书招纽磷。……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希宪力言不可,乃止。会亲王合丹及汪良臣、八春等合兵復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得二叛首以送,枭之京兆市。”
《李忽兰吉传》:“中统元年,德臣子惟正袭总帅,至青居。五月,忽兰吉等赴上都。时浑都海据六盘山以叛,世祖遣忽兰吉亟还,与汪良臣发所统二十四州兵追袭之。十月,从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纳忽石温之地,力战,杀浑都海等於阵,余党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巩昌後元帅,赐金币、鞍马、弓矢。九月,火都叛於西蕃点西岭,汪维正帅师袭之,至怯里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诏宗王只必铁木儿,以答刺海、察吉里、速木赤将蒙古军二千,忽兰吉将总率军一千,追袭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
《赵阿哥潘传》:“(赵阿哥潘)子重喜,始给侍皇子阔端为亲卫。……中统四年,从讨忽都、达吉、散竹台等,克之,只必帖木儿王承制,使袭父职为元帅。入觐,赐金虎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
《世祖纪一》:“(中统元年)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刺忽儿、合丹、忽刺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儿、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儿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自是岁以为常。”
《世祖纪二》:“(中统四年)八月,甲子,以西凉经兵,居民困弊,给钞赈之,仍免租赋三年。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丙寅,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
《世祖纪三》:“(至元二年)九月丁亥,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十一月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
《世祖纪四》:“(至元九年)十一月壬戍,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地理志三》:“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世祖纪九》:“(至元二十年)冬十月,癸卯,诸王只必帖木儿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不许。……十一月,丁已,诸王只必帖木儿请於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役,从之。”
《食货志三·岁赐》:“太宗子阔端太子位: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户,计丝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户,计钞一千九百九锭。”
以上所选材料十一则,可以分为四类,透过复杂的现象,从中追寻隐没的历史,我们解读到以下的内容:
首先,关陇战役的情况。中统元年三月,世祖即位,四月一日设立了总领全国政事的机构中书省,也称都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五月,下令设置十路宣抚司,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路之下设府、州、县。并拉开了关陇之战的序幕。4则史料中,关陇战役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交代的十分清楚。关陇战役的地域在西凉府,只必帖木儿的镇守领地。材料均提到其人。执毕帖木儿、只必铁木儿即只必帖木儿,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早已考证过。译音无定字。这是《元史》中译名不一贯的习惯所致。中统伊始以来,频称只必帖木儿为“西土亲王”“宗王”和“王”,客观的表明:在忽必烈争位以前,只必帖木儿就是蒙古宗室的诸侯王,继承了阔端的世袭封地。
其次,赏赐情况。第5则就是一张赏赐表,均是忽必烈争权称汗中的拥立者宗王、讨伐阿里不哥有功者和皇亲国戚。西凉府是兄弟二人进行争位内战的重要境域,也是饱受战火蹂躏的重灾地区。人民屡经苦难,穷困至极。而统治集团成员的只必帖木儿王是获得利益最多者之一,得到赏赐优厚者之一。
再次,王府的修筑和永昌路的设立。忽必烈创设了宗王统兵出镇和行省治理庶事相结合的体制。统制云南、甘肃、陕西、扬州、漠北等边徼要地。中统四年(1263)阴历五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沿用宋、金旧制,继设立中书省后,再设枢密院专管全国军务,改变了此前蒙古国军队由大汗、宗王、万户长、千户长自领兵马,各自为战的军事领导体制。
枢密院长官——院使——由皇太子兼领,只是虚衔;实际长官是副使二人,由史天泽、忽刺出担任,下设佥书枢密院事一员。为了适应对南宋军事行动的需要,还专门在地方上设立了“行枢密院”,相当于省军区司令部,负责指挥作战,管理当地军务。担任行枢密院知院的大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不能任此职。王府和官署是两个不相混淆的机构系统。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永昌府。”即是赐名称为永昌王王府,是府邸,是避暑宫殿,而不是永昌县的官署机构。西夏统治时期为“永州”。
永昌王是镇守封地的诸侯,并非中书省或行省所辖的永昌行政机构的成员。“新城”是对“旧城”相对而言的。是对阔端原在皇城滩的驻夏“斡耳朵”——“一个帐和车的宫殿”而言的。阔端系后王在原“行帐”地域修筑新城宫殿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古代就有以故王牙帐建城的事情。如果“永昌府”是基层官署机构的话,就是“设置”“建立”,而不会是恩赐。诸侯王修府邸,在《元史》中不乏其例。《诸王表》载:“忙哥刺,至元十一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十五年薨。”安西王忙哥刺是忽必烈的正后所生的第三子。至元九年被封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京兆便是关中,是忽必列为皇子时的封地。在安西王府宫殿没有建筑以前,安西王就在浐河之西有规模盛大的王帐。安西王府宫室的修治,大概是至元十一年(1274)开始的。据《元史》,是年安西王忙哥刺加封秦王,诏命京兆尹赵炳“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赵炳传》)
以此可以佐证:永昌王修筑的是王府。并在“新城”竣工的时间上也与安西王府建筑的时间相近。时隔六年,“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实属自然。永昌路治所在永昌城内,不仅有官署机构,当然还有王府。只必帖木儿的驻冬之所在城里,驻夏则在皇城滩的避暑宫殿。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在甘州路的甘州(今张掖)。入驻中原的蒙古诸王,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俗,所到之处就有“行帐”“行宫”。永昌路的区域,就是宋初元初的西凉府。
最后,阔端及其后王所得的封地情况。他们不仅有窝阔台时期的“分地二十四城”“岁赐”,并有丙申年(1236)的山东东平路的五户丝分地;还有忽必烈时期的湖广行省常德路的江南户钞分地,可谓优厚之至。
清代学者钱大听治学范围很广。史学上校勘考订古代史籍的文字、典章、史实,著有《廿二史考异》。在此名著《元史》部分,对永昌王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颇有独到的见解。在《地理志三》“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条中案语云:“世祖纪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永昌王即只必帖木儿也。《诸王表》无永昌王之名,盖当时以地名称之,未有赐印。”又在《耶律希亮传》“定宗幼子大名王”条中案语云:“《宗室表》,定宗三子,长忽察大王,次脑忽太子,次禾忽大王。此大名王当即禾忽也,因其分地在大名,即以为王号,犹只必帖木儿称永昌王也。”据《元史·地理志一》记载:“大名路,唐魏州。五代后汉改大名府。金称天雄军。元因旧名,为大名府路总管府。贵由幼子禾忽亦以地制名大名王。”钱氏之论,确为精辟。
钱大听又在其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详论:“元常德路铸造祭器题字,正书四行,其文云:‘常德路达鲁花赤哈珊黑黑,铸造祭器壹佰二十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凉州儒学永宝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志。’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而常德路属湖广行省,本不相统,此西凉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铸造,非常例也。
《诸王表》不载永昌王名号,唯《世主纪》: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然则《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儿也。只必帖木儿为太宗第二子阔端太子之子,见于《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载,其时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无它文可证矣。《食货志》:阔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拨江南户钞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户。是常德为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铸祭器之事。”
关于蒙古汗国的封赐情况,在《元史·诸王表》中说的较为清楚:“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规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後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初制简朴,位号无称,确是蒙古汗国游牧民族入驻中原前期的真实情况。也可从《宗室世系表》《岁赐篇》的笼统记载中看出,仅称太子、大王、王而已。至少在铁木真、窝阔台、贵由、蒙哥四朝是如此。赐爵名称的具体化,位号有称是忽必烈既定天下,大封宗亲为王时开始的,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完善的。《多桑蒙古史》也说:“成吉思汗轻视亚洲君主所习用之尊号,曾命其后裔勿采用之。所以继承诸人仅称曰汗,或可汗。诸宗王可径称其主之名,此名在书信及封册中,毫无何种荣号附丽其间。”
综上所述,我们推定,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以地为名的永昌王。
一 阔端是窝阔台汗封授的西凉王
《元朝秘史》《元史·本纪》记载: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草原上分裂的局面。太祖元年(公元1206),蒙古各部实现统一,铁木真作为各部共主,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自大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古汗国。
蒙古建国后,为了加强和巩固蒙古汗国的内部统一,成吉思汗着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权组织机构。
首先,设置了蒙古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札鲁忽赤”,蒙古语意即“大断事官”,相当于“丞相”的职务,负责处理民户分配和司法诉讼,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委任其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
其次,继续完善十进制军政管理体制,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全部蒙古人以千户为单位加以整编,打破了原来的氏族或部落组织形式。
同时,为了确保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将护卫军扩充至上万人,包括精选出来的一千名宿卫、八千名散班和一千名箭筒士。护卫军负责保护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他的幼子拖雷负责护卫军的组织、指挥及兵马的装备。另外委任忽必来为最高军事长官,称作“军事那颜”。
土地分封制也是维护蒙古统治集团的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因此,建国后就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属于大汗。
成吉思汗本人及后妃,直接控制着怯绿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又因为蒙古人在帐幕里居住,所以建立了“斡耳朵”制,“斡耳朵”蒙古语意为宫帐。成吉思汗设置了四个斡耳朵,将皇后和妃子们分别安排在其中。大汗的私人财富,也分属四个斡耳朵;大汗死后,其财富由四个斡耳朵分别继承。这一制度为历代蒙古大汗所承袭。
随后,成吉思汗以家族中血缘亲疏为标准,同时参考功劳的大小对土地进行了分配。在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为“黄金家族”,他的正后孛儿帖所生的四个儿子又被誉为“汗国宫廷的四根栋梁”。他任命长子术赤掌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管法律,三子窝阔台治理朝政,四子拖雷负责护卫。除了拥有至高的权力地位之外,王子们同样拥有各自的“兀鲁思”,意即“国中国”。在各自的封地内,诸王们拥有自主权,他们对所得的“份额”,有向子孙后代进行再分配的权力,王位也可以世袭。
成吉思汗的亲族弟兄们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铁木哥和别里古台的封地在其大“兀鲁思”东部,所以这些领主又被称为“东道诸王”。至此,蒙古汗国的统治体制、制度及法令逐渐完善起来。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一切,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他要用武力去征服周边的领域。
从此,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又长期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用兵,是对夏、对辽、对金、对宋,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对西方的用兵,则从中国境内远到中亚、欧洲。太祖四年(1209),蒙古军进攻西夏,西夏战败,纳女请和。畏兀儿人慑于蒙古军的威势,于五年遣使归顺。十三年,蒙古军灭掉了西辽。从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西征。蒙古侵略军首先灭掉了花刺子模,占领了中亚、伊朗和阿富汗的大片领土。接着,又大败俄罗斯联军于乌克兰境内的迦勒迦河。七年后回军东归蒙古。在西征回军途中,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派军随从西征及不送质子为借口,于太祖二十一年(1226)大举进攻西夏。蒙古兵分两路,成吉思汗亲率一路十万大军由漠北南下,越过黑水、贺兰山,直取武威,歼灭西夏军主力。另一路从西域出发,经哈密地区东进,攻取敦煌、酒泉、张掖。二十二年(1227)八月,在强大的蒙古铁骑攻击下,西夏政权灭亡。这一年二月,术赤病殁在咸海北方草原的封地深处,比他父亲先死六个月,时年47岁。四月,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八月病逝于秦州清水县西江驻地大帐中,在位22年,享年66岁。在汗位虚悬的两年中,幼子拖雷监国摄政。按照蒙古习俗,幼子又曰“斡惕赤斤”(灶主),可继承父母的财产而守家帐。所以,拖雷号称“也可那颜”(大官人),得以掌握成吉思汗的宫帐、牧地、怯薛护卫和大部分千户。拖雷有十一子。王妃唆鲁和帖尼所生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留名于史籍。
根据蒙古大汗的继承制度,大汗生前示意或指定某子孙继位,死后再召集亲王驸马、将相大臣参加库里尔台(部落议事制度)大会,共同推举新大汗。在蒙古语中,“库里尔台”是“盛大聚会”的意思。成吉思汗病逝两年后的太宗元年(1229)秋,蒙古诸王诸将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了库里尔台选汗大会。大会争议40日而不能决定人选。汗廷内恪守旧制的拖雷麾下的宿将老臣们主张继立统军最多的拖雷,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此时术赤已死,在二兄察合台的鼎力扶持下,经过耶律楚材和速不台等的劝说,大会才达成协议,承认成吉思汗的遗愿,推选窝阔台为大汗。
太宗十三年(1241)十一月,窝阔台酒后得病,十二月崩于行殿,终年56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由其遗孀长妻或幼子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由于窝阔台的正宫孛刺合真皇后无子,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也死去。身为诸子之母的脱列哥那——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摄政五年(1242-1246)。乃马真氏称制元年,察合台病殁封地。到此时成吉思汗的诸子已经相继谢世,孙辈叱咤风云的时刻即将来临。
定宗元年(1246)七月,蒙古汗廷在和林举行库里尔台选汗大会。金顶大帐内争论激烈。会上,有人提出失烈门(阔出长子)曾是窝阔台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应当即位。阔端以成吉思汗曾一度提到要他做汗位继承人为由,也站出来争位(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记载)。但是,在称制者六皇后乃马真氏的主持操纵下,大会以失烈门尚处幼年,阔端体弱多病为由,否定了他们。在乃马真氏的提议坚持下,宗王贵族们选定窝阔台长子贵由为汗位继承人。八月即位,是为定宗。贵由继立,在位三年,而猝然死去。时年43岁。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热衷追逐权力,积极介入蒙古汗廷残酷的争权斗争,于1249年称制,临朝视事三年,不得令终。
窝阔台有七个儿子,即贵由、阔端、阔出、哈刺察儿、合失、合丹、灭里。前五子的生母是六皇后乃马真氏,后二子的生母是业里讫纳妃子。
窝阔台即位后,把自己的几个儿子相继封王。未登汗位以前,他的草原领地在叶迷立和霍博一带。即位后,以上封地授予长子贵由。又将中原西夏故地封授给次子阔端。其他子孙驻牧于漠北窝阔台汗四季行宫附近。成吉思汗给诸子封授千户军队时,三子窝阔台受封五千户,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六十多个千户的军队和部众。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妃子继续掌管他麾下的军队、部众和封地,并抚育四个儿子。此时,窝阔台汗未和宗亲商议,擅自将拖雷系所辖的逊都思部二千户和雪你惕部一千户拨给皇子阔端,窝阔台系宗王拥有的蒙古千户数总计应在八千户以上。
窝阔台执政时期采取的多方面政策措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汗国的政权建设,也为提高大汗的地位,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合《元史·食货志》丙申(1236)年的具体记载,我们得到明晰的数据:平阳府41000多户分配给术赤系;太原府47000多户划归察合台系;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又分得大名府的68000多户,次子阔端又分得东平府的48000多户;真定路的80000多户分给拖雷系;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忽兰皇后所生)分得河间府的45000多户……
阔端,《元史》无传。称为“阔端太子”,即“阔端皇子”。又译作扩端、阔丹、库腾等。凉州地方志碑铭中多称也燀火端王、果诞王等。这是由于音译使然。阔端有五子:灭吉里歹、蒙哥都、只必帖木儿、帖必烈、曲列鲁。
窝阔台继位后,就派阔端镇抚秦、蜀、吐蕃等地,“开府西凉”,称西凉王。他逐步招抚了四川地区的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并任命许多吐蕃首领为边州长官。
太宗七年(1235),窝阔台举行了忽里尔台大会,决定了“长子出征”东欧和阔端、阔出等进兵宋境的军国大事。阴历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大举南侵。东路军由宗王口温不花率领,进攻江淮地区;中路军由阔出率领,进攻汉水及长江流域;西路军由阔端率领,进攻四川。
东路军于阴历六月征伐江淮,到十一月接连攻陷淮西的光州、蕲州、舒州。进攻真州时,被南宋的知州邱岳置炮设伏击败,收兵北还。
中路军于阴历七月初进兵唐州,开始大规模入侵襄汉地区。太宗八年,蒙古军占领襄阳。不久,因为蒙古主将阔出战死,襄阳又被宋军收复。
战事初起,西路军迅速出凤州取沔州,但是,在蜀北咽喉青野原被宋将曹友闻击退。太宗八年(1236),蒙军调集50万兵力,再次大举进攻四川,宋军被迫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阴历九月,蒙军破阳平关,宋将曹友闻战死。随后,蒙古军长驱入蜀,一月之间,连续占领成都、利州、潼州三路的绝大部分州郡,兵民惨遭焚掠屠杀。当年冬,蒙军主力撤出四川,部分军队进抵长江北岸后退兵。九年,阔端引兵北上,驻扎凉州,经营吐蕃。
《元史·赵阿哥潘传》云:“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藏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皇子阔端之镇西土也,承制以阿哥昌为迭州安抚使。”《高智耀传》又云:“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国。……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復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欲奏官之,不就。”《孟德传》亦云:“太宗即位之八年,诸王阔端命德为元帅,佩金符,领济南军攻宋徐州、光州,降其众而有其地。”从这些记载看出:阔端在皇族中的特殊地位和镇抚河西时的握权之重。
窝阔台执政十三年后病死。壬寅(1242)年春,乃马真后临朝摄政。皇子阔端依旧“开府凉州,承制得专封拜”(《新元史》),继续镇守西凉。
明崇祯十六年(164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成《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此书详细记载了从西藏有史以来直至顾实汗之间,所有历代王朝事记和王嗣传统。书中记载:“汗(成吉思汗)有子嗣多人,一子名阿阔台。台有二子名贵由和阔端。阔端皇子曾遣多达那布西征入藏,其攻战之术,虽大自天亦生畏惧,而以之加诸藏地,故金藏莫不为之慑服……并遣使回到王庭。称言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若以今生圆满福报而论,此赡部洲如成吉思汗之所受享,再无过者。倘求后世有利,则应迎致佛教大师,宜讲解脱和一切种智之道,最关紧要。未久,使臣返藏,携有迎请萨迦班智达之函扎,及下达萨迦法主之敕令。甲门来到萨迦,宣王旨意。”“继后,师应霍尔汗王之命,前往汉霍等地,故能于此殊方绝域,以不可计量之身、语、意三密事业,光显如来之圣教也。适汗王为地祗龙神所祟,师作至上无畏之布施,使其解脱疾苦。……最后,大师庄严之化身,则收入于此幻化寺中而圆寂也。”这些记述,与史实基本相符。“赴霍尔汗王之命”即“赴西凉阔端大王之命”。
太宗十一年(1239)秋,蒙古大将多达那布等奉阔端之命领兵进入前藏。在前往藏区的途中遇到藏族民众和武装僧人的反抗,双方发生冲突,各有伤亡。蒙古军杀害了几百名僧人,并烧毁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此后,多达那布在藏区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次年,他返回凉州,将了解到的西藏社会状况、地方僧俗势力及各教派的情况,向阔端作了汇报,并呈《请求迎谁为宜的详禀》,建议迎请萨班作为代表,来凉州磋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阔端采纳了多达那布的建议。
乃马真后三年(1244)八月,阔端再次派遣多达那布入藏。这次多达那布是以金字使者的身份前往,以多尔斯衮为正使组成使团。他们带着阔端的《邀请诏书》和许多礼物来到西藏(见《萨迦世系史》)。
为了雪域民众的安危和长远利益,萨班接受了阔端的邀请。于乃马真后三年底,不顾63岁的高龄,携其侄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以及精通五明的一些学者,从后藏萨迦起程,经过两年的艰辛跋涉,至五年(1246)八月抵达凉州。但此时的阔端远在蒙古高原的和林参加推举贵由继任大汗的会议,萨班未能见到阔端。直到定宗二年(1247)年初,阔端从和林返回,他们终于在凉州会面。
这一年,萨班与阔端分别作为西藏僧俗各界代表和蒙古汗国代表,就西藏归顺问题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史称“凉州会盟”。经双方磋商,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由萨班给卫藏各僧俗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一起归顺,这就是著名的《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信中详述了归顺与否对于佛法和世俗权力的利害关系,以及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派官设治、交纳贡赋、萨迦与其他官员僧俗共管西藏事务等意见,奠定了至元十六年(1279)以后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行政管理的基础,萨迦派由此也取得了卫藏地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地位。
宪宗元年(1251)阴历六月,在蒙古本土三河源头的阔帖兀阿兰之地召开了忽里尔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术赤系、拖雷系诸王、东道诸王,以及一部分察合台系诸王和窝阔台的六子合丹、七子灭里、孙子蒙哥都。虽然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多数后裔不参加会议进行抵制,但大会仍然如期举行。蒙哥得到术赤之子拔都、别儿哥相助,登上了蒙古汗国第四任大汗的宝座,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家族。成吉思汗的子孙间开始了内讧和杀戮,蒙古汗国内部出现了裂痕。《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即位伊始,蒙哥汗就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负责人选都重新作了安排。特意命同母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政大权,治理蒙古、汉地民户,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区等都属忽必烈管辖。宪宗二年八月,蒙哥汗“驻跸和林。分迁诸王於各所:合丹於别石八里地,蔑里於叶儿的石河,海都於海押立地,别儿哥於曲儿只地,脱脱於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於没脱赤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於军营。”合丹、灭里,皆窝阔台之子。海都,合失子;脱脱,哈刺察儿子;蒙哥都,阔端子;皆窝阔台之孙。乞里吉忽帖尼,窝阔台三皇后。失烈门,阔出子,窝阔台孙,后被投水溺死。也速即也速蒙哥,察合台子。孛里(不里),察合台孙,实际被杀。和只(忽察)、纳忽(脑忽),贵由子,窝阔台孙。也孙脱,察合台孙。别儿哥,蒙哥即位时的拥立者,术赤次子。蒙哥汗毫不留情地追究、肖弱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后王等反对其即位的势力,严厉惩罚企图发动政变的堂兄弟们。前摄政皇后海迷失被审后缝入一个口袋投水淹死。失烈门的生母合答失赤,贵由汗的亲信、镇守波斯军队最高统帅野只吉带以及失烈门、脑忽和忽秃黑(哈刺察儿子)三王的亲信七十多人,也因参与夺权密谋而被处死。窝阔台诸后妃的家赀也被分赐给拖雷系亲王。
随后,窝阔台汗国被划分为六个小王国,使窝阔台家族不能形成威胁汗位的力量。分别由合丹、灭里、脱脱、海都等治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他的旧部,另委亲王统带。只有阔端诸子仍保留封地和军队。但剥夺了阔端独治吐蕃的权力。不久,蒙哥汗下令处死了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也速蒙哥,由哈刺旭烈兀接任察合台汗国的可汗。
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记载:当窝阔台合罕家族的成员谋叛蒙哥合罕时,他们的军队都被夺走了,除阔端诸子的军队以外,全部被分配掉了。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蒙哥汗是将窝阔台系宗王的千户军队由原先的八千户削减至三千户。阔端诸子的三千户军队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所属的逊都思部等军队与拖雷家族关系密切,致使阔端诸子对蒙哥汗等一直十分友好。
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记载:1252年8月,蒙哥到达和林,在那里,他完全制服了他的敌人,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追究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罪状,在这以前,她一直是被宽恕的……窝阔台系只有两支,例外地没有遭到迫害,这就是阔端与合丹。合丹对于‘密谋’丝毫没有参与,他和忽必烈关系很密切,将来成为忽必烈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另外,阔端的儿子们曾主动地及时到达蒙哥那里向他致以应尽的敬礼。
《多桑蒙古史》亦载:“……谪窝阔台诸子于各地,夺其父所遗之部兵,以畀翊戴无贰心之诸王。惟合丹灭里二王及阔端诸王早诚心归命,不仅未夺其兵,且各以窝阔台之斡耳朵一所,后妃一人赐之。蒙哥究违命诸臣,遣使至各地,凡附窝阔台系者,皆逮治之。”
经过汗位争夺战,窝阔台和察合台系诸王势力倍受打击,而蒙哥和拔都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因此,蒙哥即位后,蒙古汗国主要掌控在拖雷系和术赤系诸王的手中。窝阔台系这一支血脉就衰落了,仅保留了一块“窝阔台后王封地”。拉施特说:“自此不幸时代以后,蒙古遂受内乱之害,诸王似忘成吉思汗和睦保国之遗训。”
至此,“黄金家族”的内部斗争得以平息,蒙哥通过对异己势力的严厉镇压,巩固了汗位,开始着手处理国事。
宪宗元年,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享年70岁。他的16岁的侄子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五祖。根据阔端的意旨,在凉州幻化寺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灵塔,以安葬萨班的灵骨。
就在同一年末,阔端也病殁于凉州。据清初蒙古族史家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记载:阔端于蒙哥元年(1251)去世,时年46岁。从《元史》中也可看出,阔端的行事重点在窝阔台执政和乃马真氏称制时期,蒙哥即位后渐趋消失。因此判断:《蒙古源流》的说法是可信的。
阔端病死后,蒙哥汗诏命阔端长子蒙哥都承袭西凉王王位,镇守河西。自此以后,西凉王受忽必烈亲王节制。蒙哥都的事迹,曾在《元朝秘史·长子出征》一节的叙述中出现。宪宗八年(1258),蒙哥汗征宋攻蜀的战争中,蒙哥都随征于西路军。十一月,“诸王蒙哥都攻礼义山不克”;九年,“诸王蒙哥都復攻渠州礼义山”。
明宣德五年(1430),由国师锁南监参募集资金,对幻化寺进行了重修。《重修凉州百塔志》碑文中云:“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百塔,不知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也燀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撤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焚,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曰:庄严。……”碑文中的人名“也燀火端王”即阔端,“撤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均为同一人名的异译。《中华大字典》释文为:“燀,党旱切,音亶(胆),旱韵。”蒙古语“亦(也)赫(燀)”是汉语“大”的意思。凉州“也燀火端王”就是“凉州大阔端王”,即凉州阔端大王。
清康熙年间,再次重修幻化寺,并立碑记载。《重修白塔碑记》中云:“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翻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果诞王”即阔端王;“板只达”即萨迦班智达;“乌斯藏”即卫藏,指今天的西藏。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阔端不是永昌王,而是窝阔台汗封授的以地制名的西凉王、凉州大王。
二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永昌王宪宗元年末,阔端在凉州病故。长子蒙哥都承袭西凉王,镇守其父河西封地。二年八月,蒙哥汗下令分迁诸王到各驻所时,将凉州大王蒙哥都迁徙至“扩端所居地之西”,那里有窝阔台的世袭领地。阔端的河西封地又命其三子只必帖木儿镇守。在祁连山的南麓北麓,直至焉支山下的广阔草原上设有蒙古汗国的皇家牧场,为汗廷供给了无数的优良战马。阔端驻牧设帐,驻夏行宫在永昌皇城滩,驻冬之所在西凉府。因此,只必帖木儿的镇所设在永昌。三年(1253),蒙哥汗以中州封宗亲,赐封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
宪宗六年(1256)春,蒙哥汗在蒙古中部举行忽里尔台会议,诸王移相哥、驸马也速儿等提议尽快征伐南宋。蒙哥汗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对这次亲征南宋,蒙哥汗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幼弟阿里不哥和皇子玉龙答失留守和林,主持蒙古汗国庶政,管理漠北千户军队和诸斡耳朵宫帐。进攻南宋的军队分为东、西、南三路。东路军由诸王塔察儿率领,攻略荆襄。因进军不利,改派忽必烈统领,侵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西路军随蒙哥汗出发,进攻川蜀。西凉袭王蒙哥都随征。南路军是兀良合台所率的云南蒙古军和蛮焚军一万三千,进攻路线是经广西、贵州趋潭州(今长沙)。三路军队总数10余万,试图对南宋实施三面围攻,这显然是一次旨在灭亡南宋的战略性大进军。
蒙哥汗于八年(1258)阴历十月取道汉中抵达利州。在巩昌总帅汪德臣的协助下,蒙哥所统军队渡嘉陵江和白水江,攻取地势险要的苦竹隘。又沿嘉陵江东下,拔南宋潼川府治长宁山城,招降阆州大获城及运山、青居、大良等城。年底,蒙古军顺嘉陵江南下,欲进攻南宋在四川的大本营重庆。没料到在重庆北的钓鱼山遇到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
九年阴历二月,蒙哥汗在扫清外围之后,亲自督促蒙古军和汉军对钓鱼城展开强攻。但连续攻战五个月,损兵折将,未能破城。连为蒙哥充当御前先锋的汪德臣,也在攻城时负伤“感疾”而亡。七月,蜀川一带暑热难忍,军中瘟疫流行。蒙古军只好暂时停止对钓鱼城的进攻,转而南攻重庆。而蒙哥竟在转移营地途中,病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时年52岁,在位9年。蒙古军丧失主帅,随征军除汪氏和纽磷的军队留下外,其余都随蒙哥的儿子阿速台从重庆府、合州等地撤兵北返。
蒙哥汗猝死以后,蒙古人停下了西征的脚步,也终止了南侵宋朝的行动。然而,在周边世界得以喘息之时,蒙古的权贵们却又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内斗。
蒙哥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这就为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留下了空间。
统领漠南中原事务之后,忽必烈打破蒙古部族的传统统治政策,起用儒者,尝试“以汉法治汉地”。宪宗六年春,忽必烈决定改革在桓州、抚州间设帐而居的状况,下令在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修筑新城,营建宫室房舍,三年后建成,定名为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作为王府常驻之所。开平府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地区之间,地势冲要,既便于与和林的大汗相联系,也有利于控制中原。开平的兴建,显示忽必烈以儒臣治理汉地的统治方式已初见成效。
中统元年(1260)阴历三月,忽必烈抵达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在诸王的建议下,忽必烈在开平自行召开了忽里尔台大会。
在塔察儿的提名和推举下,忽必烈登上了大宝之位,年46岁。四月,颁即位诏于天下,宣称:“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
四月,阿里不哥在哈刺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也召开了选汗的忽里尔台会议。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多数是成吉思汗直系的西道各支宗王。在这一部分蒙古汗廷宗王和权臣们的拥立下,阿里不哥也称汗即位。
这样,蒙古汗国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分别是拖雷的两个儿子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二人曾经派出许多急使,进行谈判和交涉。但因双方互不相让,未能达成协议,只能诉诸武力。
关陇之战的序幕是在中统元年(1260)五月拉开的。
蒙哥汗亲征川蜀时,曾留浑都海部4万骑兵屯戍六盘山。他攻打合州殁于钓鱼山之后,随他进攻南宋的蒙古军和汉军大部分由他的儿子阿速台统领,向北移动。阿里不哥即命部将阿蓝答儿为阿速台所领这支军队的主帅。浑都海率所部军队离开六盘山,西渡黄河,直趋甘州。阿蓝答儿自和林率军南下接应,遂与浑都海会合。阿蓝答儿、浑都海遂合军东攻西凉府只必帖木儿王领地。
八春、汪良臣二军奉命西去御敌,与浑都海军相持两月,未见分晓。九月,合丹大王及诸王哈必赤、阿曷马等率骑兵参战,会同八春、汪良臣部与阿蓝答儿、浑都海在甘州东删丹附近的耀碑谷展开决战。
忽必烈委任西道诸王合丹为全军统帅,统一号令指挥,分三路以迎敌。合丹列阵于北,八春列阵于南,汪良臣列阵于中。时值大风吹沙,天色阴晦,汪良臣命令军士下马,用短兵器突然袭击敌军左翼,绕出阵后,又击溃右翼。八春直捣敌军前部,合丹指挥精锐骑兵截断敌军归路,大败敌军,斩阿蓝答儿和浑都海,杀伤俘虏不计其数。只有部分残军逃回到吉儿吉思——阿里不哥的封地。
为了震慑敌人,稳定局势,京兆等路宜抚使廉希宪命令将阿蓝答儿、浑都海枭首于京兆(西安)示众三日。关陇之战遂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西土悉平。
随后,忽必烈立即转入主战场,就以成吉思汗的嫡孙和拖雷诸子的兄长身份乘胜去逐鹿蒙古本土漠北,统军进攻和林,亲征昔木土,大获全胜。战胜了阿里不哥,夺回了漠北的控制权,证明自己是合乎蒙古传统的大汗。
中统五年(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不得不南下归降忽必烈。第二年秋天,阿里不哥病死。
为了庆祝阿里不哥的归降和蒙古汗国的重新统一,是年八月,忽必烈特意将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以示否往泰来和鼎新革故之义。
至元元年(1264)八月,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废除“大蒙古”国号,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之意)。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灭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经过以上历史脉络的梳理,具体问题渐趋显现,为我们解读史料铺垫了基础。现将《元史》中有关资料列录如下:
《按竺迩传》:“中统元年,世祖即位,亲王有异谋者,其将阿蓝答儿、浑都海图据关陇。时按竺迩以老,委军於其子。帝遣宗王合丹、哈必赤、阿曷马西讨。按竺迩曰:‘今内难方殷,浸乱关陇,岂臣子安卧之时耶?吾虽老,尚能破贼。’遂引兵出删丹之耀碑谷,从阿曷马,与之合战。会大风,昼晦,战至晡,大败之,斩馘无算。按竺迩与总帅汪良臣获阿蓝答儿、浑都海等。捷闻,帝锡玺书褒美,赐弓矢锦衣。”
《廉希宪传》:“诏以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浑都海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阿蓝答儿復自和林提兵与之合,分结陇、蜀诸将,又使纽磷兄宿敦为书招纽磷。……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希宪力言不可,乃止。会亲王合丹及汪良臣、八春等合兵復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得二叛首以送,枭之京兆市。”
《李忽兰吉传》:“中统元年,德臣子惟正袭总帅,至青居。五月,忽兰吉等赴上都。时浑都海据六盘山以叛,世祖遣忽兰吉亟还,与汪良臣发所统二十四州兵追袭之。十月,从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纳忽石温之地,力战,杀浑都海等於阵,余党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巩昌後元帅,赐金币、鞍马、弓矢。九月,火都叛於西蕃点西岭,汪维正帅师袭之,至怯里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诏宗王只必铁木儿,以答刺海、察吉里、速木赤将蒙古军二千,忽兰吉将总率军一千,追袭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
《赵阿哥潘传》:“(赵阿哥潘)子重喜,始给侍皇子阔端为亲卫。……中统四年,从讨忽都、达吉、散竹台等,克之,只必帖木儿王承制,使袭父职为元帅。入觐,赐金虎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
《世祖纪一》:“(中统元年)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刺忽儿、合丹、忽刺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儿、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儿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自是岁以为常。”
《世祖纪二》:“(中统四年)八月,甲子,以西凉经兵,居民困弊,给钞赈之,仍免租赋三年。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丙寅,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
《世祖纪三》:“(至元二年)九月丁亥,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十一月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
《世祖纪四》:“(至元九年)十一月壬戍,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地理志三》:“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世祖纪九》:“(至元二十年)冬十月,癸卯,诸王只必帖木儿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不许。……十一月,丁已,诸王只必帖木儿请於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役,从之。”
《食货志三·岁赐》:“太宗子阔端太子位: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户,计丝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户,计钞一千九百九锭。”
以上所选材料十一则,可以分为四类,透过复杂的现象,从中追寻隐没的历史,我们解读到以下的内容:
首先,关陇战役的情况。中统元年三月,世祖即位,四月一日设立了总领全国政事的机构中书省,也称都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五月,下令设置十路宣抚司,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路之下设府、州、县。并拉开了关陇之战的序幕。4则史料中,关陇战役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交代的十分清楚。关陇战役的地域在西凉府,只必帖木儿的镇守领地。材料均提到其人。执毕帖木儿、只必铁木儿即只必帖木儿,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早已考证过。译音无定字。这是《元史》中译名不一贯的习惯所致。中统伊始以来,频称只必帖木儿为“西土亲王”“宗王”和“王”,客观的表明:在忽必烈争位以前,只必帖木儿就是蒙古宗室的诸侯王,继承了阔端的世袭封地。
其次,赏赐情况。第5则就是一张赏赐表,均是忽必烈争权称汗中的拥立者宗王、讨伐阿里不哥有功者和皇亲国戚。西凉府是兄弟二人进行争位内战的重要境域,也是饱受战火蹂躏的重灾地区。人民屡经苦难,穷困至极。而统治集团成员的只必帖木儿王是获得利益最多者之一,得到赏赐优厚者之一。
再次,王府的修筑和永昌路的设立。忽必烈创设了宗王统兵出镇和行省治理庶事相结合的体制。统制云南、甘肃、陕西、扬州、漠北等边徼要地。中统四年(1263)阴历五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沿用宋、金旧制,继设立中书省后,再设枢密院专管全国军务,改变了此前蒙古国军队由大汗、宗王、万户长、千户长自领兵马,各自为战的军事领导体制。
枢密院长官——院使——由皇太子兼领,只是虚衔;实际长官是副使二人,由史天泽、忽刺出担任,下设佥书枢密院事一员。为了适应对南宋军事行动的需要,还专门在地方上设立了“行枢密院”,相当于省军区司令部,负责指挥作战,管理当地军务。担任行枢密院知院的大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不能任此职。王府和官署是两个不相混淆的机构系统。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永昌府。”即是赐名称为永昌王王府,是府邸,是避暑宫殿,而不是永昌县的官署机构。西夏统治时期为“永州”。
永昌王是镇守封地的诸侯,并非中书省或行省所辖的永昌行政机构的成员。“新城”是对“旧城”相对而言的。是对阔端原在皇城滩的驻夏“斡耳朵”——“一个帐和车的宫殿”而言的。阔端系后王在原“行帐”地域修筑新城宫殿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古代就有以故王牙帐建城的事情。如果“永昌府”是基层官署机构的话,就是“设置”“建立”,而不会是恩赐。诸侯王修府邸,在《元史》中不乏其例。《诸王表》载:“忙哥刺,至元十一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十五年薨。”安西王忙哥刺是忽必烈的正后所生的第三子。至元九年被封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京兆便是关中,是忽必列为皇子时的封地。在安西王府宫殿没有建筑以前,安西王就在浐河之西有规模盛大的王帐。安西王府宫室的修治,大概是至元十一年(1274)开始的。据《元史》,是年安西王忙哥刺加封秦王,诏命京兆尹赵炳“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赵炳传》)
以此可以佐证:永昌王修筑的是王府。并在“新城”竣工的时间上也与安西王府建筑的时间相近。时隔六年,“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实属自然。永昌路治所在永昌城内,不仅有官署机构,当然还有王府。只必帖木儿的驻冬之所在城里,驻夏则在皇城滩的避暑宫殿。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在甘州路的甘州(今张掖)。入驻中原的蒙古诸王,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俗,所到之处就有“行帐”“行宫”。永昌路的区域,就是宋初元初的西凉府。
最后,阔端及其后王所得的封地情况。他们不仅有窝阔台时期的“分地二十四城”“岁赐”,并有丙申年(1236)的山东东平路的五户丝分地;还有忽必烈时期的湖广行省常德路的江南户钞分地,可谓优厚之至。
清代学者钱大听治学范围很广。史学上校勘考订古代史籍的文字、典章、史实,著有《廿二史考异》。在此名著《元史》部分,对永昌王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颇有独到的见解。在《地理志三》“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条中案语云:“世祖纪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永昌王即只必帖木儿也。《诸王表》无永昌王之名,盖当时以地名称之,未有赐印。”又在《耶律希亮传》“定宗幼子大名王”条中案语云:“《宗室表》,定宗三子,长忽察大王,次脑忽太子,次禾忽大王。此大名王当即禾忽也,因其分地在大名,即以为王号,犹只必帖木儿称永昌王也。”据《元史·地理志一》记载:“大名路,唐魏州。五代后汉改大名府。金称天雄军。元因旧名,为大名府路总管府。贵由幼子禾忽亦以地制名大名王。”钱氏之论,确为精辟。
钱大听又在其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详论:“元常德路铸造祭器题字,正书四行,其文云:‘常德路达鲁花赤哈珊黑黑,铸造祭器壹佰二十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凉州儒学永宝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志。’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而常德路属湖广行省,本不相统,此西凉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铸造,非常例也。
《诸王表》不载永昌王名号,唯《世主纪》: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然则《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儿也。只必帖木儿为太宗第二子阔端太子之子,见于《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载,其时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无它文可证矣。《食货志》:阔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拨江南户钞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户。是常德为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铸祭器之事。”
关于蒙古汗国的封赐情况,在《元史·诸王表》中说的较为清楚:“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规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後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初制简朴,位号无称,确是蒙古汗国游牧民族入驻中原前期的真实情况。也可从《宗室世系表》《岁赐篇》的笼统记载中看出,仅称太子、大王、王而已。至少在铁木真、窝阔台、贵由、蒙哥四朝是如此。赐爵名称的具体化,位号有称是忽必烈既定天下,大封宗亲为王时开始的,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完善的。《多桑蒙古史》也说:“成吉思汗轻视亚洲君主所习用之尊号,曾命其后裔勿采用之。所以继承诸人仅称曰汗,或可汗。诸宗王可径称其主之名,此名在书信及封册中,毫无何种荣号附丽其间。”
综上所述,我们推定,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以地为名的永昌王。
附注
参考文献:
[1]佚名撰·鲍思陶点校《元朝秘史》,齐鲁书社版。
[2]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校点本。
[3]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西藏人民出版社版。
[4]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元史》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5]张澍辑录·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三秦出版社版。
[6][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钺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版。
[7][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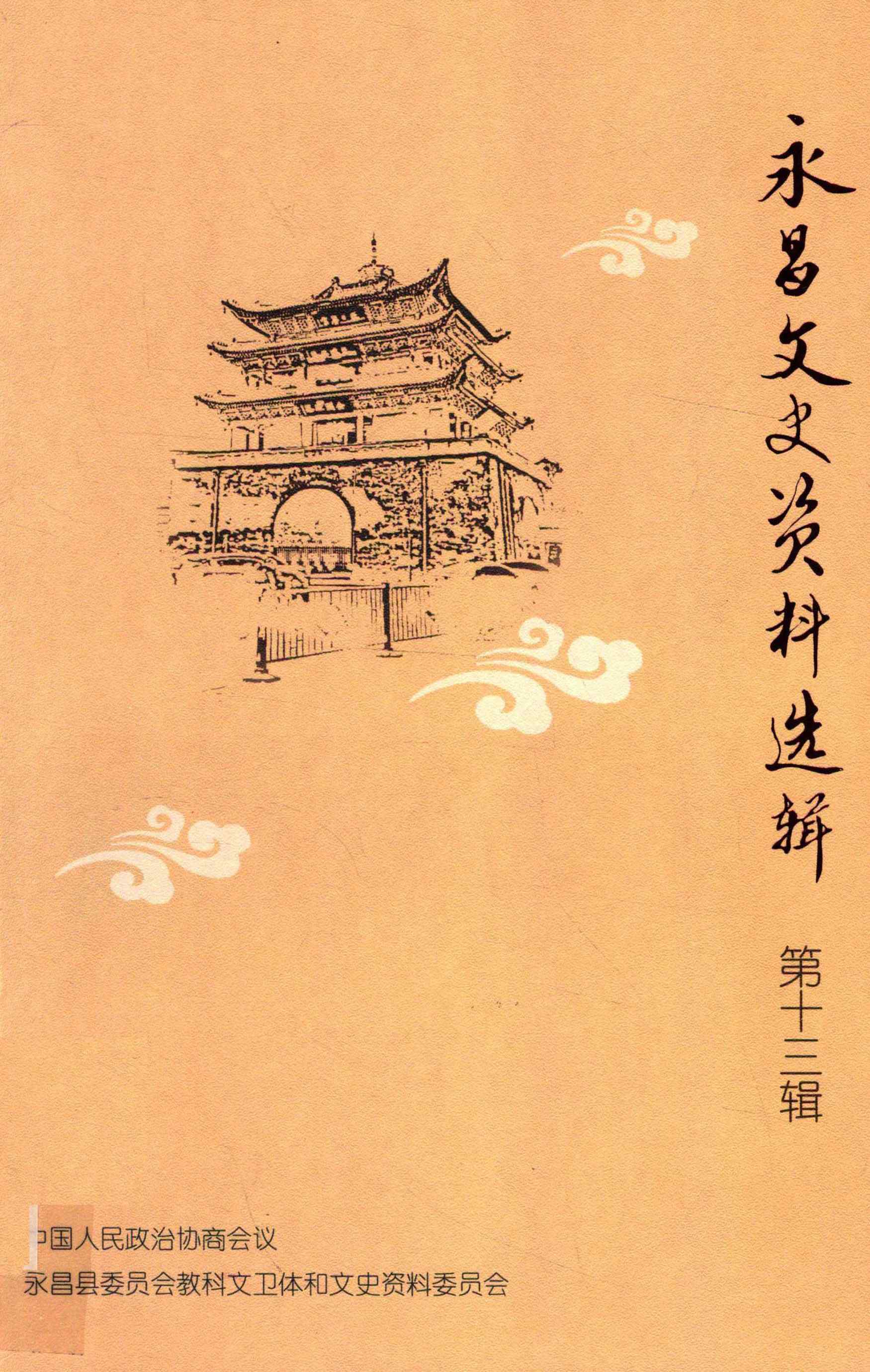
《永昌文史资料选辑》
本书共分历史文化篇、考古文化篇、文学文艺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篇、党史与西路军专题五个部分,内容总体布局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辑录了永昌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文物、文艺作品乃至亲历者的口述史,图文并茂,力求真实而生动地再现永昌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也必将是一部爱国主义和优秀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阅读
相关人物
管林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