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典型——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
| 内容出处: | 《焦家庄农业合作社史料》 图书 |
| 唯一号: | 292020020220000967 |
| 颗粒名称: | 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典型——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 |
| 分类号: | F306.4 |
| 页数: | 40 |
| 页码: | 1-40 |
| 摘要: | 本书记述了金昌市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发展状况,内容包含了组织起来力量大 合作生产有办法,自力更生渡“三荒”开展备耕创“四好”等。 |
| 关键词: | 焦家庄 合作社 典型 |
内容
在永昌县城以西的一块不足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1936年冬至1952年春的16年间,曾发生过两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停留永昌期间,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的指示,红军指战员在永昌境内创建了13个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及其群众抗日团体,在这块土地上率先组建了西十里铺、水磨关两个村苏维埃政府。祖祖辈辈深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从漫漫长夜中见到光明,男女老少全力以赴支持红军,支援革命。然而时间不久,当红军西进转移后,反革命势力即开始围剿革命,大肆搜捕、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永昌人民特别是焦家庄的群众,再度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甘肃省的土地改革试点正在进行中,翻身得解放的焦家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冲破旧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又率先组织起来,开展合作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第一个人数多、规模大、层次较高的焦家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反响强烈,意义重大,显示了她极其旺盛的生命力。走合作化道路,鼓舞了农民的志气,避免了土改后在农村可能发生的新的两极分化,改变了这里严重存在的贫困落后面貌,为全县、全省的农业合作化工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可贵经验。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成为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
40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冷静地回顾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全面研究和探讨它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深化当前的农村改革,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组织起来力量大 合作生产有办法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于1952年2月5日。是在土地改革后,未经自营而直接建立起来的甘肃省第一个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辖区东起距永昌县城西7里的柳沟,西至距永昌县城西25里的锁环沟,南依中坝渠,北靠甘新公路,是一个东西长18里、南北宽1.5里的狭长地带。辖区内有3个自然村,原分别属于城关区四、六乡。共317户,1697人。可耕地面积9050.6亩。
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大都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过着“做活牛一般,吃饭狗一般,睡觉猪一般”的贫困生活。据1951年对其中两个村247户的调查,占总人口12.6%的11户地主,就占有50.8的土地,人均占地19.3亩。仅谢青云一户地主就占有土地2395亩。而占总人口41.4%的131户雇农,只占有9.23%的土地,人均有1.06亩贫瘠地。由于地主全部采用雇工剥削的经营方式,所以耕畜、农具和房屋亦大量集中在地主手中。(见下表)
1951年,焦家庄进行了土地改革。所有制变了,主要生产资料由地主占有的相对集中变成了个体农民分散占有的形式。然而,分配到农民手中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却不能满足个体生产的需要,生产和生活仍然存在严重困难。鉴于这种情况,中共武威地委提出了在永昌县焦家庄试办合作生产的设想。1951年9月,地委书记王俊派干部到焦家庄初步了解情况,并向群众宣传农业合作问题。11月,报经省委同意,中共武威地委选派房俊峰、于竹山等一批县、区级干部先后进驻焦家庄,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筹建工作。
实行合作生产的好处一经宣传,饱尝过旧社会艰辛的贫苦农民都乐于接受,纷纷表示愿意组织起来走合作生产的道路。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合作生产也存在着一定的顾虑:贫雇农怕入社后不目由,生活不方便;中农因自已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怕和贫雇农合作吃亏;也有些人怕合作生产苦乐不均、分配不公、多劳不能多得。为了解除农民对合作生产的各种顾虑,建社干部联系实际,进行算帐对比,结合农民的既得利益,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及其伟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组织原则,决定各户在入社后就近留少量自留地,解决吃菜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组帮助解决了一个合作生产组的分配问题,对解除群众顾虑起了积极的作用。1951年春减租反霸时,将没收反革命分子的650亩地,暂时交给城关24户贫民合伙耕种,因缺乏组织领导,又无恰当的分配办法,从种到收只有少数人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多数人住在城里,偶而出城劳动一天半天就回去了,还有个别人只出城看了一两次。而在秋后分配粮食时,却平均每户分4斗小麦,形成了苦乐不均、多劳不能多得的状况。焦家庄群众目睹了这种现实,对合作生产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消极印象。为挽回不良影响,工作组帮助他们将尚未分配的葫麻,按劳分配,从而使大部分农民消除了顾虑,表示愿意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集体生产。11月5日至10日,有173户农民首批加入了合作社(其中雇农106户,贫农33户,中农6户,其他——主要是手工业者28户)。又经过不断宣传教育,原先思想动摇的51户,于11月20日至25日第二批加入了合作社(雇农22户,贫农15户,中农7户,其他7户)。就在此时,气侯突变,中坝渠冻结,3000多亩耕地尚未灌上冬水。建社干部动员已入社的农户,组织400多个劳力,集体突击破冰放水,使全部应灌水的耕地都灌上了冬水,为来年生产打下了基础。破冰放水这件事,不但在焦家庄,就在山水灌区内也是破天荒的。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说:“打冰这事,不说我74岁没见过,就是人老几辈也没听说过”。人和自然较量并且能够取胜,这对个体农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却在组织起来后实现了。这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现实的教育,加上建社干部积极领导入社农民进行冬季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取得了显著效益,于是,在12月初,有43户农民第三批加入了合作社(雇农26户,贫农3户,中农13户,其他1户)。到1952年1月,加入合作社的共达328户,1774人,入社土地8720亩。3个自然村入社户数占总户数的99.6%,入社土地占总数的92.2%。此时,合作社的筹建工作基本就绪。
1952年2月5日,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入社的328户农民,象欢庆盛大节日一样,敲锣打鼓参加合作社成立大会。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何承华,中共武威地委书记王俊,武威专署副专员孟浩及永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亲临祝贺并讲了话。大会正式宣告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暂行章程》(草案)。合作社直属武威地委领导。
《社章》(草案)规定,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定社内重大事项,选举和撤换管理委员会成员;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的领导与执行机构,由财务、宣教、技术、水利、监察等委员分工负责,集中领导。管委会推选主席(主任)1人,副主席(副主任)1至2人,负责全面工作。根据耕种方便,浇水方便,有利团结的原则,全社分成3个生产大队,15个生产小组。以生产小组为基本生产单位和分红单位,负责组织领导生产,搞好评工记分和收益分配工作。
自力更生渡“三荒”开展备耕创“四好”
建社初,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资金缺乏,生产资料不足。入社农户80——90%严重缺粮,不能下地生产。有人用歌谣反映当时的困境:“牛没麻渣马没料,毛驴乏得趺扁跤,犁地的饿得直不起腰,放羊的冻得满山跑。”如何迅速采取措施发展生产,解决社员的衣食问题,体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成了摆在于部和社员面前的大事。经讨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广大社员群众,发挥组织起来的优势,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
(一)自救渡荒
1951年冬和1952年春夏两季,合作社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人、畜、地“三张口”,口粮、饲料、种子严重缺乏。全社缺乏口粮的有174户,占总户数的51%;缺乏饲料的耕畜152头,占总耕畜的75%;有1000亩耕地没有种子,占播种面积的18%。灾荒最重的第三大队,无粮户竟占全队户数的83%。面对如此困境,合作社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如何战胜冬、春、夏“三荒”,搞好当年生产?社员们提出了“老牛破车疙瘩绳,勒紧裤带向困难作斗争”的响亮口号。合作社因势利导,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单纯依赖政府救济和听天由命等消极错误思想,确定了亲邻相帮、互助互济和组织人畜力搞副业生产的渡荒措施。一是互助互济,开展自由借贷。
困难较轻的一、二大队,动员手工业者和有余粮的农户,用自由借贷的形式帮助缺粮的社员。在铁工潘发兰的带动下,一大队23户人家一次就借出人民币32万元(旧币,下同)、铁铲子110把、烧煤300装(每装约120斤)、小麦1.08石、山药2.9石、其他杂粮7.5斗。这些钱粮,解决了32户160人12天的口粮。二大队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全队仅有15户人家有口粮。尽管如此,也有13户从自家并不充余的口粮中借出禾禾9.5斗、山药4斗、糜子3.5斗,解决了34户153人5天的口粮。三大队困难严重,几乎没有一家有余粮,但也有个别社员如周玉德,在自已很拮据的情况下借出一斗大麦帮助断炊户以解燃眉之急。自由借贷的钱粮,全部用来互相周济,解决断粮户的困难,秋后由承借人归还。二是组织力量搞工副业生产。在驻社干部动员支持下,各大队社员利用冬闲拔芨芨、拧绳、搓草腰到武威等地去卖;利用春耕结束后的空隙到祁连山挖药材、打茅柴出售或兑换粮米渡日。为给社员搞副业提供方便,合作社还建立推销站,帮助推销产品,寻找副业门路。在副业生产中,社员有什么困难,合作社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使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仅全社组织起的3个大车组、9个驮运组、3个人力组,在一个月内就收入了1725万元。此外,合作社集体经营4座油坊、1处炭窑、1座瓷窑、1处粉坊。炭窑、瓷窑的产品赊销给社员驮运到永昌县城及武威等地出售、兑换粮食。油坊加工的油品除在本地销售外,还雇上汽车拉运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去销售,解决了销路不畅、产品积压的问题,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经努力,全社副业收入当年就达到9549万元,平均每户29万元。这不仅为社员渡过“三荒”起了辅助作用,也为发展集体生产创造了条件,用副业收入款一次就从山丹买来绵羊2604只,壮大了集体的经济实力。
1952年收益分配结束后,上级担心合作社经营手工业作坊,雇用技术工人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把贩运油品等视为资本主义商业投机,加以否定,压抑了工副业生产的积极性。1953年除经营2座油坊外,其它作坊、瓷窑、炭窑全部停业,全年副业收入减少到3714万元,比1952年减少61.08%。三是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展自救。鉴于合作社的严重困难,当时政府也给一部分救济粮。但合作社把单纯的救济转变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产自救,向政府和社外借贷资金和粮食,同时还发扬“勒紧裤带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大量挑野菜掺和着有限的粮米渡日,1升(4市斤)青稞子就能解决5口之家一天的口粮。大部分社员一天只吃两顿野菜糁子汤,有的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既使这样,社员们也没有吃掉一粒种子,没有动用一两饲料,挺着腰肝胜利地渡过了难关,保证了农业生产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二)“四好”备耕
在组织社员大搞生产自救的同时,合作社为搞好第一个春耕,提出了“四好”备耕措施,即粪土收拾好,籽种准备好,牲口喂养好,农具修理好。各组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增产措施。计划每亩麦田上粪18车,每亩禾田上粪5—10车。为完成上述计划指标,全社掀起了一个积肥热潮,社员们垫圈、掏炕灰、扫草末子。队里统一组织人畜力驮羊粪,十多天就驮回790多驮。到3月底各队都完成了积肥任务。种子缺口大,社员已有的,各户均进行登记,不论多少,全部借给合作社,秋后加上适当的利息还给各户。尚缺60石小麦种子和40石其他作物种子,由县人民政府批准借给,秋后归还。耕畜由各户自喂,参加生产使役,按役力强弱情况分值。役畜不足的,由社队贷款购买或社员自行添置。这样,当年就新增加118头,基本上保证了春耕的需要。社员的大农具,作价归社,统一分配给各组使用,不足部分由合作社集体购置,小农具自备。
“四好”备耕工作的开展,打好了春耕生产的基础。建社的第一个春耕就搞得热火朝天,不仅保质保量完成了春播任务,而且由于肥料充足,还减少了轮歇地,扩大了播种面积165.1亩。
(三)统筹劳力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使用劳力方面,一开始就很注意发挥个人的特长,非常重视调动每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内有一批手工业者,把他们组织起来,修理制造农具。由于集体为他们发挥专长创造了条件,他们积极性很高。如铁匠潘发兰、赵文学、杨培荣等经过努力钻研,仿制了7寸步犁和其它农具,解决了农具不足的问题。对农活很不内行的小商、小贩等,将他们按职业性质编组进行副业生产,发挥了他们的一技之长,在渡过“三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妇女是“半边天”,可是,在解放前,这里的妇女很少参加农业劳动。建社后,合作社宣传男女平等,改变轻视妇女的传统习俗,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并认真贯彻实施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这样,极大地激发了妇女们参加劳动的热情,成了合作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四)改进耕作方法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有几大特点:面积大。建社前播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58.2%,大量可耕地轮歇荒芜;土质贫瘠,卧牛石多,俗有“车烂牛王宫”之说;南高北低,倾斜度大,呈梯田式递降。当地农民习惯于粗放耕作,广种薄收,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很低。建社后,为提高产量,合作社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一是平整土地。一开始,这项工作只是有重点地分期分批进行,先从甘新公路沿线开始,清除卧牛石,减小倾斜度,防止水土流失。当社员群众认识到平整土地的优越性后,便有计划地组织劳力利用每年秋收后的时机大量平整,为以后的机耕奠定了基础。到1954年,全社机耕面积已达1783亩,1955年达2468亩,占总耕地的32.74%。二是兴修水利。中坝是全社的水利命脉,从西向东横贯合作社全境。合作社多次组织人力挑修中坝,每次参加劳力在200人以上,占整个修坝劳力的60%。另一方面,通过平田整地,改修了一些斗渠,浇水方式由过去的大水串灌改为分渠分块灌溉,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三是推广良种。过去,焦家庄的种子大多为红伙穗、白坚口、红光头、白疙瘩。因长期种植,品种严重蜕化、混杂,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产量低。建社第一年,省农林厅给合作社调拨了一批小麦良种“774”、“96”、“玉皮”,由薛兰斌厅长亲自送到焦家庄,经试种,当年获得了大丰收,以后加以推广。四是精耕细作。建社初,政府就派农业技术人员长期驻社,指导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变当地长期沿用的粗放耕作习惯。改大扬种为溜种,进而使用播种机条播;减少“白水”种植,实行合理施肥、追肥并试用推广化肥;加强田间管理,锄草、防治病虫害,增强作物的抗伏、抗病、抗旱能力;改进耕作工具,使用新式步犁、畜力播种机、收割机等先进的农机具。
(五)扩种“撞田”①
合作社以南,祁连山北麓,是土质肥沃、面积广袤的者来坝滩,只要雨水充沛,春天墒情好,即可抢种。过去群众就有种“撞田”的习惯。1952年,合作社从山丹培黎学校借来小型拖拉机,在者来坝滩种“撞田”500多亩,当年获得好收成,打粮食6万多斤。1953年又种了1100多亩,并试铺了沙地,秋后收获粮食20多万斤。
多打粮食增收入 巩固集体作贡献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畜牧业和工副业的大力发展,用短短的4年时间,就转变了贫团面貌,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显示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其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建社前的1951年,各种原粮总收入是64.8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03斤。建社后的头一年(即1952年),全社播种面积7449.7亩,粮食总产量达107万斤,比1951年增产65.2%,平均亩产达到143.7斤,比1951年提高了38.8%。这个产量与当时和合作社条件相同的互助组、自耕农相比,分别提高29.5和36.7%。1953年是建社的第二年,全社播种的8007亩农作物普遍丰收,粮食总产量达140多万斤,比1952年增产37万多斤,比建社前的1951年翻了一番。
(二)社员生活明显改善
建社前的1951年,焦家庄人均有粮403斤。1952年建社后,当年达到666斤,比1951年增加了65.3%。全社93以上的农户总收入比1951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53年人均有粮1209斤,1954年1149.5斤,1955年达1260斤。加之生产成本逐年降低,除去贷款和各项开支,社员的实际收入逐年增加,很快地摆脱了缺吃少穿的贫困处境。如社员丁玉明,解放前家中一无所有,靠人力贩柴维持一家3口人的生活,家无隔夜粮,身无二件衣。土改中他家分到土地21亩,牛6/10(即6分)头,褐大衣一件。1952年合作时,精肚子穿一件大衣,夫妻合穿一条裤子,小孩子无论冬夏,只穿一个破毛背心。合作第一年夏天锄草时,组内社员们帮凑着给他老婆缝了一条裤子,才能出门参加劳动。年终分红时,他家分得各种原粮近10石(约4000斤),除负担公共开支和归还债务外,虽缺3个月口粮,但比合作前好多了。1953年分红时分得各种原粮13.9石(5560多斤),扣除公共生产开支留足全年的口粮后,还卖给国家余粮687斤,3口人缝了里面三新的三套棉衣和一床紫哗叽被子,买了一条新白毡、一匹红骟马。又如社员张国玺,中农,全家13口人,男女主要劳力4人,有牛6头、马5匹。合作前生活虽能过得去,可家无存粮,早年泥好的3个仓子,从没有装满过粮食。合作后,由于劳、畜力较多,第一年分红就分得各种原粮54.6石,除负担公共开支,归还借贷外,还剩余10多石粮食(仓子仍然没装满)。1953年他家分红分得各种原粮68石,给国家出售余粮15石,购买绵羊67只,剩余的粮食,那3个仓子还装不下。老俩口高兴地说:“20多年的愿望,合作起来才实现了”。
(三)集体经济实力日益雄厚
初建社时,全社有牲畜113头(主要是牛、驴),大车30辆,犁107付。建社的当年,就新增耕畜118头(主要是骡马),羊700只,大车24辆(包括运输胶轮车10辆),新式步犁118张。到1953年,除耕畜继续有所增加外,羊发展到3000只,还购置了双轮双铧犁、双把犁铧、钉齿耙、三齿耘锄、七吋和十吋步犁等新式农具42部。到1955年,全社共有马123匹,牛244头,驴188头,骆驼6峰,羊3217只;马拉式新式农具(播种机、收割机)112部,铁轮车38辆;公共积累已达242833元(新币下同),集体经济实力愈加雄厚。
(四)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1953年12月,正当宣传统购统销销政策之时,合作社一次就卖给国家余粮44万多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9%,人均给国家卖粮280多斤。社员们说:“合作社的路,就是幸富的路,我们一定要多卖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爱国行为,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的高度赞扬,省委书记张德生亲自致电嘉勉。1954年给国家卖余粮33万多斤。1955年卖46万多斤。
(五)合作社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
由于合作社经济效益明显,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建社初,有的社员怀疑:“合作社究竟能不能多打粮食?多打了以后,又能不能多分?”加之,合作社的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欠完善,有个别社员提出退社(1952年9户,1953年7户)合作社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一原则,允许他们退出,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搞好生产。如一大队社员张正祥,1952年冬天退了社,次年春,种子撒在地里没有畜力耕种,每天只好睡在地里打麻雀,最后还是合作社帮了他的忙。1953年分配后,张正祥又入了社。其他退社的群众,也陆续回到了合作社。合作社连年增产,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的事实,充分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也教育了原来思想动摇的社员和周围的群众。尤其是利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集体的力量优势帮助周围自耕农、互助组和其他合作社解决生产中发生的问题,邀请他们参加合作社的有关会议,促进了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也发挥了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点带面的典型引路作用。
实事求是讲效益 按劳分配求发展
合作社的创立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从建立、巩固到发展无不遵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其组织形式、规模大小、经营方针、核算单位和分配原则的确定,都要符合实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
(一)组织原则
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团结自愿参加合作事业的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劳力、土地、耕畜、农具、水利、技术,共同劳动,发挥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发展农业生产,逐步采用先进经验,技术,使用新式农具,克服个体经营的落后性,扩大生产,为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为达到上述目的,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合作社的组织原则规定如下:
(1)土改后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完全自愿参加。
(2)实行合作经营、民主管理,全部生产果实为参加合作社的成员所有并按劳分配。
(3)适合当地实际情况与经济特点。
实践证明,自愿互利,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正确的。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社员有入社、退社自由”。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立,地、县工作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向群众实事求是地讲明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他们自愿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1953年分红后,曾有个别农户因不同原因退了社,但后经社内外生产活动、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对比,觉得合作社确实比单干优越得多,又重新回到了合作社,并且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富、还得走合作的路。”这个事例充分体现了合作社自愿互利的组织原则,同时也说明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和实际效益,是农民自愿入社的根本原因。
(二)收益分配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生产资料折股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员对生产资料占有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不正确处理好生产资料的报酬问题,就会使部分社员感到自已参加合作生产吃亏。为此,合作社采取了按入股土地分租和按劳分红的分配办法。建社第一年,实行比例分红,在总收入中扣除公粮(农业税)、籽种、肥料、农具等项开支后,以25%作为土地分租,75%按劳分配。土地分租的方法是将各种不同质量的土地折合成一个标准亩,再按各户标准亩数分租,这是社员易于接受的办法。1953年分配时,从上年分租比例,当地一般租额和土地负担等三方面加以对比,经民主公议,确定每一标准亩固定地租6升半(约26斤)主粮。此标准在通常年成不变,但遇歉收年,随劳动报酬的降低,可适当降低土地租额,以保证减产后的劳动日分红。按劳分配部分,除了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所得劳动日分红外,牲口(自喂公役)使役也计工分红。这种分配原则,评工方法的制定及其执行,也是经过实践,逐步调整完善的。合作社刚成立时,有些组无代价的使用人力、畜力送粪,引起了劳、畜力多的社员不满。春耕开始后,即改为按件评工记分的办法,根据当地普通劳动水平,每人每天完成一定数量质量的农活后记1个劳动日,超额增分,不足扣分,基本上做到了合理计算社员劳动日。牲畜使役记工,一开始订得过高,冬春使役一天,骡马计20分,牛15分。这又引起了人力多畜力少的社员不满。经过一段实践后,由社员讨论,将骡马使役工日压为18分,牛14分。对农具的处理办法是:大农具,如大车、犁铧、铡刀等,折价归公,三年还清价款;小农具自备自用。副业收益,除去成本外,全部盈利都按劳动日统一分配,但土地股分不能参加副业收入分配。
总之,合作社的分配原则就是,定质定量,按件记工,土地分租,畜力分红,等价互利,按劳取酬。在收益分配方面取得经验后,为激发各组的生产热情,发挥生产小组的能动作用,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合作社还制定了超产奖励的办法,规定凡小组产量超过社定增产任务,超产部分的70%归小组分配,30%归社作为生产奖金。比如:每亩小麦定产为5分,增产任务为1分,共6分,即亩收获6斗就算完成增产任务,超过6斗的部分即可按超产奖励办法执行。但是,如无客观原因,其产量低于定产者,经民主评议,予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各组还根据实际,实行小包工,段落包工,或按件记工等形式,在激发社员劳动热情,促进生产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处理公共积累方面,也是根据实际,逐步加以完善的。1952年分配时,由于公共扣留太多,社员的实际收入只占了总收入的63%,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53年分配时,合作社做了纠正,公共扣留20%,分配部分占80%,把重点放在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方面,适当照顾了扩大再生产,这样既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促进了集体生产的发展。
建立党的核心组织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省、地、县三级党委的具体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西北局的关怀和指示。在筹建过程中和建社初,武威地委和永昌县委派得力干部进驻工作。西北局曾电示,要“抽派一批县、区级干部进去工作,为了取得经验,花一批干部也有必要”。地县派出的干部,在帮助建社和搞好经营管理的同时,对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帮思想,压任务,教办法,办训练班等形式,进行培养,使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成长起来了一批骨干力量并从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建社前,焦家庄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建社后,于1952年7月1日由办社党员干部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由房俊峰担任,武宝帜任组织委员。干部支部成立后至1954年春,先后4次发展17名农民党员,又于1954年4月成立了焦家庄直属乡党支部。乡支部共有党员19名,除新入党的17名农村党员外,还有2名转业军人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担任生产、行政职务,副社主任2人,管理委员4人,生产小组长9人。支部委员会有7人组成,书记1人,由张国昌担任,生产委员2人,组织、宣传、武装、检查委员各1人。党员按照地区分为3个小组。乡支部成立后,在社内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党员学习互助合作政策和党员八项标准,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向党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和统购统销政策教育,使党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基本上划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界线,明确了农业发展方向,坚定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信心。
党支部除配合管委会领导生产,决策重大问题外,在建社干部的帮助下,还经常性地对社员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支部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根据社员群众各个时期不同思想状况,结合当时生产进行的。比如:制定增产计划,耕畜试行公有,推行小包工和进行整地等,都是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解除群众顾虑,鼓舞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保证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小农经济,发展集体生产,不断巩固和提高农业合作社。因此,这种思想教育的特点是结合实际,讲求实效。教育方式和内容丰富、灵活多样。归纳起来,党支部对社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的。
(一)社章教育
社章教育是合作社的基本政策原则教育。通过社章教育,逐步克服个体农民散漫状况,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认识,明确自身的权力和义务,加强纪律观念,并借以正确处理受益分配与生产投资的关系,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从思想和制度上保证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建社初,合作社对社员进行社章教育不够,许多社员对合作社的方针、任务、性质以及发展前途还不十分明确。后来,党支部规定把社章教育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干部冬训
干部冬训是合作社总结交流生产经验,集中社、队、组于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政治觉悟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
每年冬季,合作社利用农闲举办干部冬训班。参加培训的有管理委员会委员,党、团支部委员,各生产组骨干和积极分子。冬训中除了全面总结当年的生产经验,讨论制定来年生产计划外,着重传达学习中央、省、地县有关文件精神,不断提高办社骨干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通过学习,不仅使基层干部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而且在他们的带动下,社员们都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合作社在探索过程中少走弯路,不断发展。
(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工农联盟教育
初级农生产业合作社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生产组织。因此,各人与集体、私与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为了克服社员从旧社会带来的小私有者的生产盲目性和只图个人发家,不顾国家建设的思想,合作社经常对社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工农联盟的教育,采取组织社员、干部和工人进行联谊活动及到工厂参观等办法,激发社员爱国热情,提高社员对党和工人阶级的认识,坚定“农民只有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求得翻身解放”的思想。同时,还反复向社员讲解国家利益和农民自已利益的一致性;合作社的生产,必须服从国家需要;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相互支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等道理,逐步提高社员的爱国主义觉悟。
(四)集体主义教育
刚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社员,难以一下子摆脱小生产者的分散主义习气和狭隘思想的束缚。合作社针对这一问题,对社员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树立热爱集体、团结互助,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等新的道德风尚。
建社初,社员集体主义观念淡漠,有的对集体生产不够关心,认为啥事都有社内干部负责;有的对公共财产不够爱护,认为是大家的,不知道集体的每一损失都是个人利益的损失。为此,合作社针对实际问题,在社内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五)加强社内外团结教育
合作社相当重视“大帮小”、“社帮组”,“先进带动落后一起先进”,给周围群众做好榜样。同时要求社员克服骄傲自大、排斥单干和“合作社特殊”的思想和做法。合作社成立之后,曾帮助社外群众,改革耕作技术,兑换良种,邀请他们参观、座谈、介绍经验,有时还用马拉机帮助播种等,深受周围群众欢迎,对促进周围群众走合作化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社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支部和办社干部认真地、经常性地研究、分析各个时期社员的思想情况,从生产实际出发决定教育内容和方式,做到了有的放矢,避免了唱高调、说空话的形式主义。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教育外,还通过生产投资和收益分配,进行等价互利教育;通过制订计划,进行计划生产,克服保守思想的教育;利用重大节日或纪念活动,培养社员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教育;通过评选奖励劳动模范和评比竞赛活动,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通过新式农机具的使用和组织参观工矿单位,进行工农联盟和发展国家工业化的教育。农忙时间,为不误生产,思想教育就利用生产空隙采取地头读报、讲故事、说快板、座谈和交流生产经验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这样,不仅是社员受到教育,懂得了许多道理和常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精神上的娱乐,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
重视群众团体工作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合作社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群众团体工作。地、县委在选派工作组时,注意选派专职的青年、妇女干部和治保干部到焦家庄参加建社工作。很快培养了一批青年、妇女骨干,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妇联会和民兵组织。
各群众组织建立后,广泛发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参加生产,走合作化道路,充分发挥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建社初,在驻社干部的组织领导下,青年、妇女和民兵在生产自救、备耕、春耕生产中大显身手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焦家庄团支部成立后,青年团员李建荣、南世荣,民兵分队长张国祥等,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饥肠漉漉地带头进山驮羊粪,十多天驮回790多驮。李建荣还把自已路上吃的馍馍喂给了乏困的毛驴,自已宁肯饿着肚子,也要把羊粪送下山。在夏收中,团支部带领团员、青年龙口夺食,团员尚富学把手割破了,他还是坚持干,和其他人一样早出晚归,继续割麦子。女青年陈月英敢向男社员挑战,每天能割七、八分地,并以这样的进度坚持把麦割完。在生产第一线,团组织很重视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入团,不断壮大团组织的力量。
旧社会,焦家庄一带的贫苦农民日子虽然过得穷,可妇女们一般只在家中操持家务,很少下地干农活。解放后,妇女翻了身,她们从封建枷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特别是合作社成立后,妇联组织向广大女社员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并实施《婚姻法》,对她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妇女们的觉悟迅速提高了。她们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纷纷走出家门和男人们一起下地干活。当时,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工具简陋,妇女们就用背筐背土、背粪。除家务劳动外,妇女们还要掏炕、垫圈,到地里垒窑、煨粪,春播时选种、溜肥,夏天锄草、浇水,秋天割麦、整地,什么活都干,并且干的不比男的少。于是她们的形象在男人们眼里变得高大起来了。一开始,一些男社员轻蔑地说,婆姨们能咋乎个啥,可后来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服,感叹道:“嘿!妇女们可真了不起。”
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对传统习俗的一个冲击,是新时代的潮流。三大队女社员严金贵等向全社妇女提出挑战,对全社妇女更是一个促进。个别游手好闲的懒婆娘也坐不住了,她们自觉地加入到劳动妇女的行列之中。夏天锄草,妇女们是主力,仅1952年全社妇女共投入锄草工日就达12502个,使全社6433亩伙田普遍锄草一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逐步成了自觉行动,一次天下大雨,发了洪水,女社员孙桂林(团员)、张金花(团员)发动了五、六个伙伴,率先下水抬石头、垒石墙堵洪水,保护庄稼。被洪水冲倒的小麦,又是她们一把把扶起来,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女社员李慧英(团员)浇水时,带头跳下刺骨的冷水堵坝保苗。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思议的。
宣传实施《婚姻法》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合作社带头提倡婚姻自主,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孙桂林,在妇联会的帮助下,解除了过去的不合理婚约,和本队社员杨新华自由恋爱结了婚,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为保证妇女身体健康,省妇幼站曾派卫生队到焦家庄工作,宣传卫生常识,治疗妇女多发病,改变过去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使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深深体会到了党对妇女的关心。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后,有小孩的就感到很不方便。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大队三组有三位年近古稀的老奶奶主动办起了托儿所,为有小孩子的妇女带小孩。政府为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特意发给10多元钱,给托儿所购买玩具和食品。妇女们参加劳动后,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女社员谢秋梅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没干庄稼活,被男人看不起,时常挨打挨骂。自成立合作社后,我也参加了劳动,男人也另眼相看了。
民兵组织在合作社既是生产突击队,又担负着治安保卫工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阶级斗争表现激烈,祁连山里还出没着一些小股残匪,他们伺机搞破坏活动,扰乱社会治安。为保卫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和合作社的生产建设,社里成立了基干民兵连,由武威军分区配发给步枪20多支、子弹300多发。民兵连除维护合作社的治安外,有时还配合县公安局或全区民兵剿匪。一次,据有关情报,祁连山河沟一带有几个土匪企图到牧群中抢羊,合作社民兵受命前往警戒,保护羊群,挫败了土匪的阴谋。
扫除文盲学文化 掌握技术促生产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建社以来,就把文化学习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列入全社年度工作计划之中。特别是社内逐步使用农业机械耕作后,干部社员都认识到,没有文化是不能使用机器的,所以,要求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就越来越高。学习文化的具体工作由党支部统一安排,责成各队(分社)领导干部,布置任务,实施教学,并号召党团员和干部带头学习文化。后来,社内设立了专门领导机构,制定了学习计划,统一安排学习时间,实行检查,汇报制度,大大促进了群众性的业余文化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化学习对促进农业生产,改变社员精神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1952年春,全社成立了扫盲识字班3处,参加学习的有114人。教师都由办社工作组干部担任。1954年6月,县上派专干协助合作社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把原3个识字班建成包含9个初小班的3所常年民校,学员增加到245人,全社青壮年文盲绝大部分都上了民校。文化学习的热潮使一些老年人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报名,上了民校,一时出现了“婆媳同班”、“夫妇同桌”和“父女互教互学”的新鲜事。尽管农活劳累、紧张,但社员们似乎忘记了疲倦,着魔似的投入了业余文化学习,凡可利用的机会和时间都可不拘形式地用来练习读写。如有的社员家门口挂起了写着生字的小黑板。出门进门都要念道。类似这种既不耽误生产,又可增加读写机会,提高学习成效的方式方法应有尽有。正如当时有群众创作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快板《学文化》所述:“大地是张纸,芨芨做金笔;大腿是黑板,胳膊是笔记;白天划地皮,晚上划肚皮”。这是多么生动、朴实而又真诚、热烈的学习景象。在学习文化的群众热潮中,还涌现出了不少先进典型。如被群众称为“老积极”的尚万泰,他上学不到一月半,就识字300多个。他还现身说法,四处动员别人学习文化。胡德明受尚万泰的鼓励和动员,也积极参加学习,并向尚万泰表示决心:“老哥,你学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决不落后!”学习文化的组织形式和学习方法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的。1955年春,为了克服过分集中的学习方法所造成的缺点,便利学员学习,做到识字生产两不误,就以耕作队、生产组为单位组织识字班,在社员里面聘请识字的人担任业余教师或专职教师进行教学;学习时间定为每天晚饭后1小时半至2小时(农忙季节为1小时或放农忙假);学习内容除文化课外,还加了政治时事,文化课以新编农民识字课本为主,并有机地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技术教育,由群众教师负责教学,县上的专干进行业务指导。政治时事由工作组干部负责教学,由党支部领导。为解决社员开会、评工记分与学习文化占用时间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规定每周星期一、五学习文化,星期二、四学习政治时事,星期三评工开会,星期六党团员过组织生活。在农忙期间,提倡利用会前和生产空隙学习,实行小黑板下地,进行地头教学。
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和社员生活普遍提高,社员们深深体会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主又是不能建立在大量文盲基础上的”这个道理,学习文化的热情更加高涨。经过一年的时间,原来识字400个左右的人,己达到脱盲标准;原来的文盲,有些已识字900多个;一般学员也能识500字以上。每到夜幕降临,刚吃过饭的社员群众就涌向学习地点,夜校灯影曈曈,书声琅琅,各队都是一派挑灯夜读的景象。
文化学习还促进了合作社文娱、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初,社队成立了俱乐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文娱积极分子唱歌、跳舞,有时还表演说快板、讲故事等小节目。1955年,社内组织了业余剧团,经常演出秦腔、眉户、歌剧和话剧,活跃了社员群众的文化生活。体育方面,建社前几乎是空白,到1955年转高级社前,全社已有6个篮球场,各个生产耕作队都组织了球队。每当下午收工后,篮球场上就热闹起来。每场球赛,总有许多社员围观助兴。
文化学习和文体活动,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农民诗人赵炳虎的快板书《农业合作社就是好》、《穷沙滩变成了金银滩》等作品曾在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省级报刊上发表,开了曾是文盲的翻身农民在报刊上写文章的先例。
“高楼平地起”——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典型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共甘肃省委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的一个试点。它的建立过程是“一步登天式”的。从合作社的筹建直到转入高级社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西北局也经常给予指示,并派干部指导检查工作。在“只许办好,不许办垮”的原则要求下,派往焦家庄的办社干部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一个规模相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起来,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很高的效益,使“吃饭没锅锅,睡觉没窝窝”的焦家庄农民很快摆脱穷困,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集体积累大幅度增加,并在三年内出售余粮120万斤,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甘肃省以至西北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典型。
这样一个典型能够成功地树立起来,并且直接为全县乃至全省的合作化运动提供经验,是与当时的方针政策及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与各级领导的关怀、办社干部努力分不开的。
1951年武威地委书记王俊亲自筹划安排在焦家庄创办农业合作社,并派干部赴焦家庄做调查和宣传工作。同年10月,结合土改,地、县选派的工作组正式进行筹建。工作组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51年冬,省农业厅厅长薛兰斌到正式筹建合作社的焦家庄视察,答应给即将建立的合作社调拨小麦良种。次年春,合作社首次试种良种,取得了好收成,并为以后在推广优良品种方面打下了基础。1952年3月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在省委秘书长何承华、省农协主任安振、武威地委书记王俊等陪同下,亲临焦家庄农业社视察。邓宝珊深入社员家庭嘘寒问暖,增强了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搞好春耕的勇气。就在这一年,西北局为了搞好这个试点,派干部到焦家庄指导工作,共青团西北局宣传部干部惠庶昌驻焦家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年底合作社主任房俊峰到西北局向习仲勋同志汇报工作。1954年冬,省委书记张仲良亲临焦家庄进行了视察。中共武威地委书记王俊、徐宗望,副书记张文辉更是焦家庄农业社的常客,他们经常检查工作,有时把地委常委会议也放在焦家庄召开。此外,省、地、县的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干部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己者、作家,科研单位的学者,大学教授也常到焦家庄社进行调查研究,采访报道。如作家李千峰曾到焦家庄实地考察;作家丁杰写的《高楼平地起》,使焦家庄的事迹遐迩闻名。1954年7月,甘肃省农林厅在焦家庄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国营拖拉机站,机站建立后,即在焦家庄和其它农业社签订合同进行机耕。这对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改进耕作技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年10月,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张国昌去北京参加中央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会议,并问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汇报了工作。
驻社工作组的全体干部,在建社过程中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以身作则,不搞特殊,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办好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奋力拼搏。1951冬打冰放水时,群众怀疑:“行吗?这件事前辈人可从没干过。”工作组立即进行鼓动:“人心齐,泰山移。合作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驻社干部不光是这样热情地动员组织,更重要的是亲自带头分段包干。克服“三荒”那阵,驻社干部出主意想办法,东奔西跑,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联系、求援,寻找副业生产门路,进行生产自救。办社干部吃住都和社员一样。合作社经济连年发展,公共积累不断增加,可从领导到社员,并没有忘记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方针,从不大手大脚地花集体的钱。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来的多了,外地前来参观学习的同志多了,他们坚持因陋就简地接待,把公共积累首先用于扩大再生产。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社外群众的强烈反响。开始,他们抱观望态度,经过连续两年的增产,看见焦家庄社员一改过去的贫困面貌,他们惊诧不已,于是由原来的怀疑变为羡慕,纷纷要求仿效焦家庄,组织合作社。这充分显示了典型的力量和作用。
1955年春,正当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高潮之时,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经过研究讨论,并经上级党委批准,进行了提高社的工作(即合并分红单位,牲畜折价归公等工作),将原来的生产大队改为分社,并成立了分社管理委员会。除第一分社暂时仍实行小队(原小组)分红外,二、三分社实行以社为单位分红。分社与其下属的生产耕作队签订常年包工包产合同,年终视合同完成情况进行分配。1955年12月23日,焦家庄农业社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正式转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点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刘克文执笔)
40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冷静地回顾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全面研究和探讨它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深化当前的农村改革,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组织起来力量大 合作生产有办法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于1952年2月5日。是在土地改革后,未经自营而直接建立起来的甘肃省第一个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辖区东起距永昌县城西7里的柳沟,西至距永昌县城西25里的锁环沟,南依中坝渠,北靠甘新公路,是一个东西长18里、南北宽1.5里的狭长地带。辖区内有3个自然村,原分别属于城关区四、六乡。共317户,1697人。可耕地面积9050.6亩。
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大都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过着“做活牛一般,吃饭狗一般,睡觉猪一般”的贫困生活。据1951年对其中两个村247户的调查,占总人口12.6%的11户地主,就占有50.8的土地,人均占地19.3亩。仅谢青云一户地主就占有土地2395亩。而占总人口41.4%的131户雇农,只占有9.23%的土地,人均有1.06亩贫瘠地。由于地主全部采用雇工剥削的经营方式,所以耕畜、农具和房屋亦大量集中在地主手中。(见下表)
1951年,焦家庄进行了土地改革。所有制变了,主要生产资料由地主占有的相对集中变成了个体农民分散占有的形式。然而,分配到农民手中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却不能满足个体生产的需要,生产和生活仍然存在严重困难。鉴于这种情况,中共武威地委提出了在永昌县焦家庄试办合作生产的设想。1951年9月,地委书记王俊派干部到焦家庄初步了解情况,并向群众宣传农业合作问题。11月,报经省委同意,中共武威地委选派房俊峰、于竹山等一批县、区级干部先后进驻焦家庄,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筹建工作。
实行合作生产的好处一经宣传,饱尝过旧社会艰辛的贫苦农民都乐于接受,纷纷表示愿意组织起来走合作生产的道路。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合作生产也存在着一定的顾虑:贫雇农怕入社后不目由,生活不方便;中农因自已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怕和贫雇农合作吃亏;也有些人怕合作生产苦乐不均、分配不公、多劳不能多得。为了解除农民对合作生产的各种顾虑,建社干部联系实际,进行算帐对比,结合农民的既得利益,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及其伟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组织原则,决定各户在入社后就近留少量自留地,解决吃菜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组帮助解决了一个合作生产组的分配问题,对解除群众顾虑起了积极的作用。1951年春减租反霸时,将没收反革命分子的650亩地,暂时交给城关24户贫民合伙耕种,因缺乏组织领导,又无恰当的分配办法,从种到收只有少数人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多数人住在城里,偶而出城劳动一天半天就回去了,还有个别人只出城看了一两次。而在秋后分配粮食时,却平均每户分4斗小麦,形成了苦乐不均、多劳不能多得的状况。焦家庄群众目睹了这种现实,对合作生产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消极印象。为挽回不良影响,工作组帮助他们将尚未分配的葫麻,按劳分配,从而使大部分农民消除了顾虑,表示愿意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集体生产。11月5日至10日,有173户农民首批加入了合作社(其中雇农106户,贫农33户,中农6户,其他——主要是手工业者28户)。又经过不断宣传教育,原先思想动摇的51户,于11月20日至25日第二批加入了合作社(雇农22户,贫农15户,中农7户,其他7户)。就在此时,气侯突变,中坝渠冻结,3000多亩耕地尚未灌上冬水。建社干部动员已入社的农户,组织400多个劳力,集体突击破冰放水,使全部应灌水的耕地都灌上了冬水,为来年生产打下了基础。破冰放水这件事,不但在焦家庄,就在山水灌区内也是破天荒的。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说:“打冰这事,不说我74岁没见过,就是人老几辈也没听说过”。人和自然较量并且能够取胜,这对个体农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却在组织起来后实现了。这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现实的教育,加上建社干部积极领导入社农民进行冬季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取得了显著效益,于是,在12月初,有43户农民第三批加入了合作社(雇农26户,贫农3户,中农13户,其他1户)。到1952年1月,加入合作社的共达328户,1774人,入社土地8720亩。3个自然村入社户数占总户数的99.6%,入社土地占总数的92.2%。此时,合作社的筹建工作基本就绪。
1952年2月5日,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入社的328户农民,象欢庆盛大节日一样,敲锣打鼓参加合作社成立大会。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何承华,中共武威地委书记王俊,武威专署副专员孟浩及永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亲临祝贺并讲了话。大会正式宣告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暂行章程》(草案)。合作社直属武威地委领导。
《社章》(草案)规定,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定社内重大事项,选举和撤换管理委员会成员;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的领导与执行机构,由财务、宣教、技术、水利、监察等委员分工负责,集中领导。管委会推选主席(主任)1人,副主席(副主任)1至2人,负责全面工作。根据耕种方便,浇水方便,有利团结的原则,全社分成3个生产大队,15个生产小组。以生产小组为基本生产单位和分红单位,负责组织领导生产,搞好评工记分和收益分配工作。
自力更生渡“三荒”开展备耕创“四好”
建社初,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资金缺乏,生产资料不足。入社农户80——90%严重缺粮,不能下地生产。有人用歌谣反映当时的困境:“牛没麻渣马没料,毛驴乏得趺扁跤,犁地的饿得直不起腰,放羊的冻得满山跑。”如何迅速采取措施发展生产,解决社员的衣食问题,体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成了摆在于部和社员面前的大事。经讨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广大社员群众,发挥组织起来的优势,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
(一)自救渡荒
1951年冬和1952年春夏两季,合作社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人、畜、地“三张口”,口粮、饲料、种子严重缺乏。全社缺乏口粮的有174户,占总户数的51%;缺乏饲料的耕畜152头,占总耕畜的75%;有1000亩耕地没有种子,占播种面积的18%。灾荒最重的第三大队,无粮户竟占全队户数的83%。面对如此困境,合作社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如何战胜冬、春、夏“三荒”,搞好当年生产?社员们提出了“老牛破车疙瘩绳,勒紧裤带向困难作斗争”的响亮口号。合作社因势利导,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单纯依赖政府救济和听天由命等消极错误思想,确定了亲邻相帮、互助互济和组织人畜力搞副业生产的渡荒措施。一是互助互济,开展自由借贷。
困难较轻的一、二大队,动员手工业者和有余粮的农户,用自由借贷的形式帮助缺粮的社员。在铁工潘发兰的带动下,一大队23户人家一次就借出人民币32万元(旧币,下同)、铁铲子110把、烧煤300装(每装约120斤)、小麦1.08石、山药2.9石、其他杂粮7.5斗。这些钱粮,解决了32户160人12天的口粮。二大队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全队仅有15户人家有口粮。尽管如此,也有13户从自家并不充余的口粮中借出禾禾9.5斗、山药4斗、糜子3.5斗,解决了34户153人5天的口粮。三大队困难严重,几乎没有一家有余粮,但也有个别社员如周玉德,在自已很拮据的情况下借出一斗大麦帮助断炊户以解燃眉之急。自由借贷的钱粮,全部用来互相周济,解决断粮户的困难,秋后由承借人归还。二是组织力量搞工副业生产。在驻社干部动员支持下,各大队社员利用冬闲拔芨芨、拧绳、搓草腰到武威等地去卖;利用春耕结束后的空隙到祁连山挖药材、打茅柴出售或兑换粮米渡日。为给社员搞副业提供方便,合作社还建立推销站,帮助推销产品,寻找副业门路。在副业生产中,社员有什么困难,合作社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使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仅全社组织起的3个大车组、9个驮运组、3个人力组,在一个月内就收入了1725万元。此外,合作社集体经营4座油坊、1处炭窑、1座瓷窑、1处粉坊。炭窑、瓷窑的产品赊销给社员驮运到永昌县城及武威等地出售、兑换粮食。油坊加工的油品除在本地销售外,还雇上汽车拉运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去销售,解决了销路不畅、产品积压的问题,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经努力,全社副业收入当年就达到9549万元,平均每户29万元。这不仅为社员渡过“三荒”起了辅助作用,也为发展集体生产创造了条件,用副业收入款一次就从山丹买来绵羊2604只,壮大了集体的经济实力。
1952年收益分配结束后,上级担心合作社经营手工业作坊,雇用技术工人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把贩运油品等视为资本主义商业投机,加以否定,压抑了工副业生产的积极性。1953年除经营2座油坊外,其它作坊、瓷窑、炭窑全部停业,全年副业收入减少到3714万元,比1952年减少61.08%。三是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展自救。鉴于合作社的严重困难,当时政府也给一部分救济粮。但合作社把单纯的救济转变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产自救,向政府和社外借贷资金和粮食,同时还发扬“勒紧裤带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大量挑野菜掺和着有限的粮米渡日,1升(4市斤)青稞子就能解决5口之家一天的口粮。大部分社员一天只吃两顿野菜糁子汤,有的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既使这样,社员们也没有吃掉一粒种子,没有动用一两饲料,挺着腰肝胜利地渡过了难关,保证了农业生产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二)“四好”备耕
在组织社员大搞生产自救的同时,合作社为搞好第一个春耕,提出了“四好”备耕措施,即粪土收拾好,籽种准备好,牲口喂养好,农具修理好。各组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增产措施。计划每亩麦田上粪18车,每亩禾田上粪5—10车。为完成上述计划指标,全社掀起了一个积肥热潮,社员们垫圈、掏炕灰、扫草末子。队里统一组织人畜力驮羊粪,十多天就驮回790多驮。到3月底各队都完成了积肥任务。种子缺口大,社员已有的,各户均进行登记,不论多少,全部借给合作社,秋后加上适当的利息还给各户。尚缺60石小麦种子和40石其他作物种子,由县人民政府批准借给,秋后归还。耕畜由各户自喂,参加生产使役,按役力强弱情况分值。役畜不足的,由社队贷款购买或社员自行添置。这样,当年就新增加118头,基本上保证了春耕的需要。社员的大农具,作价归社,统一分配给各组使用,不足部分由合作社集体购置,小农具自备。
“四好”备耕工作的开展,打好了春耕生产的基础。建社的第一个春耕就搞得热火朝天,不仅保质保量完成了春播任务,而且由于肥料充足,还减少了轮歇地,扩大了播种面积165.1亩。
(三)统筹劳力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使用劳力方面,一开始就很注意发挥个人的特长,非常重视调动每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内有一批手工业者,把他们组织起来,修理制造农具。由于集体为他们发挥专长创造了条件,他们积极性很高。如铁匠潘发兰、赵文学、杨培荣等经过努力钻研,仿制了7寸步犁和其它农具,解决了农具不足的问题。对农活很不内行的小商、小贩等,将他们按职业性质编组进行副业生产,发挥了他们的一技之长,在渡过“三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妇女是“半边天”,可是,在解放前,这里的妇女很少参加农业劳动。建社后,合作社宣传男女平等,改变轻视妇女的传统习俗,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并认真贯彻实施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这样,极大地激发了妇女们参加劳动的热情,成了合作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四)改进耕作方法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有几大特点:面积大。建社前播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58.2%,大量可耕地轮歇荒芜;土质贫瘠,卧牛石多,俗有“车烂牛王宫”之说;南高北低,倾斜度大,呈梯田式递降。当地农民习惯于粗放耕作,广种薄收,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很低。建社后,为提高产量,合作社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一是平整土地。一开始,这项工作只是有重点地分期分批进行,先从甘新公路沿线开始,清除卧牛石,减小倾斜度,防止水土流失。当社员群众认识到平整土地的优越性后,便有计划地组织劳力利用每年秋收后的时机大量平整,为以后的机耕奠定了基础。到1954年,全社机耕面积已达1783亩,1955年达2468亩,占总耕地的32.74%。二是兴修水利。中坝是全社的水利命脉,从西向东横贯合作社全境。合作社多次组织人力挑修中坝,每次参加劳力在200人以上,占整个修坝劳力的60%。另一方面,通过平田整地,改修了一些斗渠,浇水方式由过去的大水串灌改为分渠分块灌溉,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三是推广良种。过去,焦家庄的种子大多为红伙穗、白坚口、红光头、白疙瘩。因长期种植,品种严重蜕化、混杂,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产量低。建社第一年,省农林厅给合作社调拨了一批小麦良种“774”、“96”、“玉皮”,由薛兰斌厅长亲自送到焦家庄,经试种,当年获得了大丰收,以后加以推广。四是精耕细作。建社初,政府就派农业技术人员长期驻社,指导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变当地长期沿用的粗放耕作习惯。改大扬种为溜种,进而使用播种机条播;减少“白水”种植,实行合理施肥、追肥并试用推广化肥;加强田间管理,锄草、防治病虫害,增强作物的抗伏、抗病、抗旱能力;改进耕作工具,使用新式步犁、畜力播种机、收割机等先进的农机具。
(五)扩种“撞田”①
合作社以南,祁连山北麓,是土质肥沃、面积广袤的者来坝滩,只要雨水充沛,春天墒情好,即可抢种。过去群众就有种“撞田”的习惯。1952年,合作社从山丹培黎学校借来小型拖拉机,在者来坝滩种“撞田”500多亩,当年获得好收成,打粮食6万多斤。1953年又种了1100多亩,并试铺了沙地,秋后收获粮食20多万斤。
多打粮食增收入 巩固集体作贡献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畜牧业和工副业的大力发展,用短短的4年时间,就转变了贫团面貌,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显示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其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建社前的1951年,各种原粮总收入是64.8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03斤。建社后的头一年(即1952年),全社播种面积7449.7亩,粮食总产量达107万斤,比1951年增产65.2%,平均亩产达到143.7斤,比1951年提高了38.8%。这个产量与当时和合作社条件相同的互助组、自耕农相比,分别提高29.5和36.7%。1953年是建社的第二年,全社播种的8007亩农作物普遍丰收,粮食总产量达140多万斤,比1952年增产37万多斤,比建社前的1951年翻了一番。
(二)社员生活明显改善
建社前的1951年,焦家庄人均有粮403斤。1952年建社后,当年达到666斤,比1951年增加了65.3%。全社93以上的农户总收入比1951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53年人均有粮1209斤,1954年1149.5斤,1955年达1260斤。加之生产成本逐年降低,除去贷款和各项开支,社员的实际收入逐年增加,很快地摆脱了缺吃少穿的贫困处境。如社员丁玉明,解放前家中一无所有,靠人力贩柴维持一家3口人的生活,家无隔夜粮,身无二件衣。土改中他家分到土地21亩,牛6/10(即6分)头,褐大衣一件。1952年合作时,精肚子穿一件大衣,夫妻合穿一条裤子,小孩子无论冬夏,只穿一个破毛背心。合作第一年夏天锄草时,组内社员们帮凑着给他老婆缝了一条裤子,才能出门参加劳动。年终分红时,他家分得各种原粮近10石(约4000斤),除负担公共开支和归还债务外,虽缺3个月口粮,但比合作前好多了。1953年分红时分得各种原粮13.9石(5560多斤),扣除公共生产开支留足全年的口粮后,还卖给国家余粮687斤,3口人缝了里面三新的三套棉衣和一床紫哗叽被子,买了一条新白毡、一匹红骟马。又如社员张国玺,中农,全家13口人,男女主要劳力4人,有牛6头、马5匹。合作前生活虽能过得去,可家无存粮,早年泥好的3个仓子,从没有装满过粮食。合作后,由于劳、畜力较多,第一年分红就分得各种原粮54.6石,除负担公共开支,归还借贷外,还剩余10多石粮食(仓子仍然没装满)。1953年他家分红分得各种原粮68石,给国家出售余粮15石,购买绵羊67只,剩余的粮食,那3个仓子还装不下。老俩口高兴地说:“20多年的愿望,合作起来才实现了”。
(三)集体经济实力日益雄厚
初建社时,全社有牲畜113头(主要是牛、驴),大车30辆,犁107付。建社的当年,就新增耕畜118头(主要是骡马),羊700只,大车24辆(包括运输胶轮车10辆),新式步犁118张。到1953年,除耕畜继续有所增加外,羊发展到3000只,还购置了双轮双铧犁、双把犁铧、钉齿耙、三齿耘锄、七吋和十吋步犁等新式农具42部。到1955年,全社共有马123匹,牛244头,驴188头,骆驼6峰,羊3217只;马拉式新式农具(播种机、收割机)112部,铁轮车38辆;公共积累已达242833元(新币下同),集体经济实力愈加雄厚。
(四)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1953年12月,正当宣传统购统销销政策之时,合作社一次就卖给国家余粮44万多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9%,人均给国家卖粮280多斤。社员们说:“合作社的路,就是幸富的路,我们一定要多卖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爱国行为,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的高度赞扬,省委书记张德生亲自致电嘉勉。1954年给国家卖余粮33万多斤。1955年卖46万多斤。
(五)合作社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
由于合作社经济效益明显,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建社初,有的社员怀疑:“合作社究竟能不能多打粮食?多打了以后,又能不能多分?”加之,合作社的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欠完善,有个别社员提出退社(1952年9户,1953年7户)合作社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一原则,允许他们退出,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搞好生产。如一大队社员张正祥,1952年冬天退了社,次年春,种子撒在地里没有畜力耕种,每天只好睡在地里打麻雀,最后还是合作社帮了他的忙。1953年分配后,张正祥又入了社。其他退社的群众,也陆续回到了合作社。合作社连年增产,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的事实,充分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也教育了原来思想动摇的社员和周围的群众。尤其是利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集体的力量优势帮助周围自耕农、互助组和其他合作社解决生产中发生的问题,邀请他们参加合作社的有关会议,促进了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也发挥了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点带面的典型引路作用。
实事求是讲效益 按劳分配求发展
合作社的创立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从建立、巩固到发展无不遵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其组织形式、规模大小、经营方针、核算单位和分配原则的确定,都要符合实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
(一)组织原则
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团结自愿参加合作事业的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劳力、土地、耕畜、农具、水利、技术,共同劳动,发挥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发展农业生产,逐步采用先进经验,技术,使用新式农具,克服个体经营的落后性,扩大生产,为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为达到上述目的,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合作社的组织原则规定如下:
(1)土改后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完全自愿参加。
(2)实行合作经营、民主管理,全部生产果实为参加合作社的成员所有并按劳分配。
(3)适合当地实际情况与经济特点。
实践证明,自愿互利,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正确的。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社员有入社、退社自由”。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立,地、县工作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向群众实事求是地讲明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他们自愿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1953年分红后,曾有个别农户因不同原因退了社,但后经社内外生产活动、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对比,觉得合作社确实比单干优越得多,又重新回到了合作社,并且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富、还得走合作的路。”这个事例充分体现了合作社自愿互利的组织原则,同时也说明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和实际效益,是农民自愿入社的根本原因。
(二)收益分配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生产资料折股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员对生产资料占有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不正确处理好生产资料的报酬问题,就会使部分社员感到自已参加合作生产吃亏。为此,合作社采取了按入股土地分租和按劳分红的分配办法。建社第一年,实行比例分红,在总收入中扣除公粮(农业税)、籽种、肥料、农具等项开支后,以25%作为土地分租,75%按劳分配。土地分租的方法是将各种不同质量的土地折合成一个标准亩,再按各户标准亩数分租,这是社员易于接受的办法。1953年分配时,从上年分租比例,当地一般租额和土地负担等三方面加以对比,经民主公议,确定每一标准亩固定地租6升半(约26斤)主粮。此标准在通常年成不变,但遇歉收年,随劳动报酬的降低,可适当降低土地租额,以保证减产后的劳动日分红。按劳分配部分,除了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所得劳动日分红外,牲口(自喂公役)使役也计工分红。这种分配原则,评工方法的制定及其执行,也是经过实践,逐步调整完善的。合作社刚成立时,有些组无代价的使用人力、畜力送粪,引起了劳、畜力多的社员不满。春耕开始后,即改为按件评工记分的办法,根据当地普通劳动水平,每人每天完成一定数量质量的农活后记1个劳动日,超额增分,不足扣分,基本上做到了合理计算社员劳动日。牲畜使役记工,一开始订得过高,冬春使役一天,骡马计20分,牛15分。这又引起了人力多畜力少的社员不满。经过一段实践后,由社员讨论,将骡马使役工日压为18分,牛14分。对农具的处理办法是:大农具,如大车、犁铧、铡刀等,折价归公,三年还清价款;小农具自备自用。副业收益,除去成本外,全部盈利都按劳动日统一分配,但土地股分不能参加副业收入分配。
总之,合作社的分配原则就是,定质定量,按件记工,土地分租,畜力分红,等价互利,按劳取酬。在收益分配方面取得经验后,为激发各组的生产热情,发挥生产小组的能动作用,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合作社还制定了超产奖励的办法,规定凡小组产量超过社定增产任务,超产部分的70%归小组分配,30%归社作为生产奖金。比如:每亩小麦定产为5分,增产任务为1分,共6分,即亩收获6斗就算完成增产任务,超过6斗的部分即可按超产奖励办法执行。但是,如无客观原因,其产量低于定产者,经民主评议,予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各组还根据实际,实行小包工,段落包工,或按件记工等形式,在激发社员劳动热情,促进生产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处理公共积累方面,也是根据实际,逐步加以完善的。1952年分配时,由于公共扣留太多,社员的实际收入只占了总收入的63%,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53年分配时,合作社做了纠正,公共扣留20%,分配部分占80%,把重点放在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方面,适当照顾了扩大再生产,这样既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促进了集体生产的发展。
建立党的核心组织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省、地、县三级党委的具体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西北局的关怀和指示。在筹建过程中和建社初,武威地委和永昌县委派得力干部进驻工作。西北局曾电示,要“抽派一批县、区级干部进去工作,为了取得经验,花一批干部也有必要”。地县派出的干部,在帮助建社和搞好经营管理的同时,对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帮思想,压任务,教办法,办训练班等形式,进行培养,使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成长起来了一批骨干力量并从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建社前,焦家庄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建社后,于1952年7月1日由办社党员干部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由房俊峰担任,武宝帜任组织委员。干部支部成立后至1954年春,先后4次发展17名农民党员,又于1954年4月成立了焦家庄直属乡党支部。乡支部共有党员19名,除新入党的17名农村党员外,还有2名转业军人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担任生产、行政职务,副社主任2人,管理委员4人,生产小组长9人。支部委员会有7人组成,书记1人,由张国昌担任,生产委员2人,组织、宣传、武装、检查委员各1人。党员按照地区分为3个小组。乡支部成立后,在社内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党员学习互助合作政策和党员八项标准,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向党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和统购统销政策教育,使党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基本上划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界线,明确了农业发展方向,坚定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信心。
党支部除配合管委会领导生产,决策重大问题外,在建社干部的帮助下,还经常性地对社员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支部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根据社员群众各个时期不同思想状况,结合当时生产进行的。比如:制定增产计划,耕畜试行公有,推行小包工和进行整地等,都是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解除群众顾虑,鼓舞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保证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小农经济,发展集体生产,不断巩固和提高农业合作社。因此,这种思想教育的特点是结合实际,讲求实效。教育方式和内容丰富、灵活多样。归纳起来,党支部对社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的。
(一)社章教育
社章教育是合作社的基本政策原则教育。通过社章教育,逐步克服个体农民散漫状况,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认识,明确自身的权力和义务,加强纪律观念,并借以正确处理受益分配与生产投资的关系,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从思想和制度上保证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建社初,合作社对社员进行社章教育不够,许多社员对合作社的方针、任务、性质以及发展前途还不十分明确。后来,党支部规定把社章教育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干部冬训
干部冬训是合作社总结交流生产经验,集中社、队、组于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政治觉悟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
每年冬季,合作社利用农闲举办干部冬训班。参加培训的有管理委员会委员,党、团支部委员,各生产组骨干和积极分子。冬训中除了全面总结当年的生产经验,讨论制定来年生产计划外,着重传达学习中央、省、地县有关文件精神,不断提高办社骨干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通过学习,不仅使基层干部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而且在他们的带动下,社员们都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合作社在探索过程中少走弯路,不断发展。
(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工农联盟教育
初级农生产业合作社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生产组织。因此,各人与集体、私与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为了克服社员从旧社会带来的小私有者的生产盲目性和只图个人发家,不顾国家建设的思想,合作社经常对社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工农联盟的教育,采取组织社员、干部和工人进行联谊活动及到工厂参观等办法,激发社员爱国热情,提高社员对党和工人阶级的认识,坚定“农民只有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求得翻身解放”的思想。同时,还反复向社员讲解国家利益和农民自已利益的一致性;合作社的生产,必须服从国家需要;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相互支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等道理,逐步提高社员的爱国主义觉悟。
(四)集体主义教育
刚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社员,难以一下子摆脱小生产者的分散主义习气和狭隘思想的束缚。合作社针对这一问题,对社员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树立热爱集体、团结互助,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等新的道德风尚。
建社初,社员集体主义观念淡漠,有的对集体生产不够关心,认为啥事都有社内干部负责;有的对公共财产不够爱护,认为是大家的,不知道集体的每一损失都是个人利益的损失。为此,合作社针对实际问题,在社内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五)加强社内外团结教育
合作社相当重视“大帮小”、“社帮组”,“先进带动落后一起先进”,给周围群众做好榜样。同时要求社员克服骄傲自大、排斥单干和“合作社特殊”的思想和做法。合作社成立之后,曾帮助社外群众,改革耕作技术,兑换良种,邀请他们参观、座谈、介绍经验,有时还用马拉机帮助播种等,深受周围群众欢迎,对促进周围群众走合作化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社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支部和办社干部认真地、经常性地研究、分析各个时期社员的思想情况,从生产实际出发决定教育内容和方式,做到了有的放矢,避免了唱高调、说空话的形式主义。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教育外,还通过生产投资和收益分配,进行等价互利教育;通过制订计划,进行计划生产,克服保守思想的教育;利用重大节日或纪念活动,培养社员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教育;通过评选奖励劳动模范和评比竞赛活动,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通过新式农机具的使用和组织参观工矿单位,进行工农联盟和发展国家工业化的教育。农忙时间,为不误生产,思想教育就利用生产空隙采取地头读报、讲故事、说快板、座谈和交流生产经验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这样,不仅是社员受到教育,懂得了许多道理和常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精神上的娱乐,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
重视群众团体工作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合作社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群众团体工作。地、县委在选派工作组时,注意选派专职的青年、妇女干部和治保干部到焦家庄参加建社工作。很快培养了一批青年、妇女骨干,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妇联会和民兵组织。
各群众组织建立后,广泛发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参加生产,走合作化道路,充分发挥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建社初,在驻社干部的组织领导下,青年、妇女和民兵在生产自救、备耕、春耕生产中大显身手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焦家庄团支部成立后,青年团员李建荣、南世荣,民兵分队长张国祥等,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饥肠漉漉地带头进山驮羊粪,十多天驮回790多驮。李建荣还把自已路上吃的馍馍喂给了乏困的毛驴,自已宁肯饿着肚子,也要把羊粪送下山。在夏收中,团支部带领团员、青年龙口夺食,团员尚富学把手割破了,他还是坚持干,和其他人一样早出晚归,继续割麦子。女青年陈月英敢向男社员挑战,每天能割七、八分地,并以这样的进度坚持把麦割完。在生产第一线,团组织很重视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入团,不断壮大团组织的力量。
旧社会,焦家庄一带的贫苦农民日子虽然过得穷,可妇女们一般只在家中操持家务,很少下地干农活。解放后,妇女翻了身,她们从封建枷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特别是合作社成立后,妇联组织向广大女社员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并实施《婚姻法》,对她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妇女们的觉悟迅速提高了。她们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纷纷走出家门和男人们一起下地干活。当时,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工具简陋,妇女们就用背筐背土、背粪。除家务劳动外,妇女们还要掏炕、垫圈,到地里垒窑、煨粪,春播时选种、溜肥,夏天锄草、浇水,秋天割麦、整地,什么活都干,并且干的不比男的少。于是她们的形象在男人们眼里变得高大起来了。一开始,一些男社员轻蔑地说,婆姨们能咋乎个啥,可后来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服,感叹道:“嘿!妇女们可真了不起。”
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对传统习俗的一个冲击,是新时代的潮流。三大队女社员严金贵等向全社妇女提出挑战,对全社妇女更是一个促进。个别游手好闲的懒婆娘也坐不住了,她们自觉地加入到劳动妇女的行列之中。夏天锄草,妇女们是主力,仅1952年全社妇女共投入锄草工日就达12502个,使全社6433亩伙田普遍锄草一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逐步成了自觉行动,一次天下大雨,发了洪水,女社员孙桂林(团员)、张金花(团员)发动了五、六个伙伴,率先下水抬石头、垒石墙堵洪水,保护庄稼。被洪水冲倒的小麦,又是她们一把把扶起来,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女社员李慧英(团员)浇水时,带头跳下刺骨的冷水堵坝保苗。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思议的。
宣传实施《婚姻法》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合作社带头提倡婚姻自主,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孙桂林,在妇联会的帮助下,解除了过去的不合理婚约,和本队社员杨新华自由恋爱结了婚,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为保证妇女身体健康,省妇幼站曾派卫生队到焦家庄工作,宣传卫生常识,治疗妇女多发病,改变过去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使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深深体会到了党对妇女的关心。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后,有小孩的就感到很不方便。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大队三组有三位年近古稀的老奶奶主动办起了托儿所,为有小孩子的妇女带小孩。政府为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特意发给10多元钱,给托儿所购买玩具和食品。妇女们参加劳动后,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女社员谢秋梅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没干庄稼活,被男人看不起,时常挨打挨骂。自成立合作社后,我也参加了劳动,男人也另眼相看了。
民兵组织在合作社既是生产突击队,又担负着治安保卫工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阶级斗争表现激烈,祁连山里还出没着一些小股残匪,他们伺机搞破坏活动,扰乱社会治安。为保卫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和合作社的生产建设,社里成立了基干民兵连,由武威军分区配发给步枪20多支、子弹300多发。民兵连除维护合作社的治安外,有时还配合县公安局或全区民兵剿匪。一次,据有关情报,祁连山河沟一带有几个土匪企图到牧群中抢羊,合作社民兵受命前往警戒,保护羊群,挫败了土匪的阴谋。
扫除文盲学文化 掌握技术促生产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建社以来,就把文化学习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列入全社年度工作计划之中。特别是社内逐步使用农业机械耕作后,干部社员都认识到,没有文化是不能使用机器的,所以,要求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就越来越高。学习文化的具体工作由党支部统一安排,责成各队(分社)领导干部,布置任务,实施教学,并号召党团员和干部带头学习文化。后来,社内设立了专门领导机构,制定了学习计划,统一安排学习时间,实行检查,汇报制度,大大促进了群众性的业余文化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化学习对促进农业生产,改变社员精神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1952年春,全社成立了扫盲识字班3处,参加学习的有114人。教师都由办社工作组干部担任。1954年6月,县上派专干协助合作社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把原3个识字班建成包含9个初小班的3所常年民校,学员增加到245人,全社青壮年文盲绝大部分都上了民校。文化学习的热潮使一些老年人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报名,上了民校,一时出现了“婆媳同班”、“夫妇同桌”和“父女互教互学”的新鲜事。尽管农活劳累、紧张,但社员们似乎忘记了疲倦,着魔似的投入了业余文化学习,凡可利用的机会和时间都可不拘形式地用来练习读写。如有的社员家门口挂起了写着生字的小黑板。出门进门都要念道。类似这种既不耽误生产,又可增加读写机会,提高学习成效的方式方法应有尽有。正如当时有群众创作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快板《学文化》所述:“大地是张纸,芨芨做金笔;大腿是黑板,胳膊是笔记;白天划地皮,晚上划肚皮”。这是多么生动、朴实而又真诚、热烈的学习景象。在学习文化的群众热潮中,还涌现出了不少先进典型。如被群众称为“老积极”的尚万泰,他上学不到一月半,就识字300多个。他还现身说法,四处动员别人学习文化。胡德明受尚万泰的鼓励和动员,也积极参加学习,并向尚万泰表示决心:“老哥,你学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决不落后!”学习文化的组织形式和学习方法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的。1955年春,为了克服过分集中的学习方法所造成的缺点,便利学员学习,做到识字生产两不误,就以耕作队、生产组为单位组织识字班,在社员里面聘请识字的人担任业余教师或专职教师进行教学;学习时间定为每天晚饭后1小时半至2小时(农忙季节为1小时或放农忙假);学习内容除文化课外,还加了政治时事,文化课以新编农民识字课本为主,并有机地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技术教育,由群众教师负责教学,县上的专干进行业务指导。政治时事由工作组干部负责教学,由党支部领导。为解决社员开会、评工记分与学习文化占用时间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规定每周星期一、五学习文化,星期二、四学习政治时事,星期三评工开会,星期六党团员过组织生活。在农忙期间,提倡利用会前和生产空隙学习,实行小黑板下地,进行地头教学。
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和社员生活普遍提高,社员们深深体会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主又是不能建立在大量文盲基础上的”这个道理,学习文化的热情更加高涨。经过一年的时间,原来识字400个左右的人,己达到脱盲标准;原来的文盲,有些已识字900多个;一般学员也能识500字以上。每到夜幕降临,刚吃过饭的社员群众就涌向学习地点,夜校灯影曈曈,书声琅琅,各队都是一派挑灯夜读的景象。
文化学习还促进了合作社文娱、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初,社队成立了俱乐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文娱积极分子唱歌、跳舞,有时还表演说快板、讲故事等小节目。1955年,社内组织了业余剧团,经常演出秦腔、眉户、歌剧和话剧,活跃了社员群众的文化生活。体育方面,建社前几乎是空白,到1955年转高级社前,全社已有6个篮球场,各个生产耕作队都组织了球队。每当下午收工后,篮球场上就热闹起来。每场球赛,总有许多社员围观助兴。
文化学习和文体活动,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农民诗人赵炳虎的快板书《农业合作社就是好》、《穷沙滩变成了金银滩》等作品曾在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省级报刊上发表,开了曾是文盲的翻身农民在报刊上写文章的先例。
“高楼平地起”——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典型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共甘肃省委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的一个试点。它的建立过程是“一步登天式”的。从合作社的筹建直到转入高级社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西北局也经常给予指示,并派干部指导检查工作。在“只许办好,不许办垮”的原则要求下,派往焦家庄的办社干部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一个规模相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起来,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很高的效益,使“吃饭没锅锅,睡觉没窝窝”的焦家庄农民很快摆脱穷困,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集体积累大幅度增加,并在三年内出售余粮120万斤,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甘肃省以至西北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典型。
这样一个典型能够成功地树立起来,并且直接为全县乃至全省的合作化运动提供经验,是与当时的方针政策及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与各级领导的关怀、办社干部努力分不开的。
1951年武威地委书记王俊亲自筹划安排在焦家庄创办农业合作社,并派干部赴焦家庄做调查和宣传工作。同年10月,结合土改,地、县选派的工作组正式进行筹建。工作组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51年冬,省农业厅厅长薛兰斌到正式筹建合作社的焦家庄视察,答应给即将建立的合作社调拨小麦良种。次年春,合作社首次试种良种,取得了好收成,并为以后在推广优良品种方面打下了基础。1952年3月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在省委秘书长何承华、省农协主任安振、武威地委书记王俊等陪同下,亲临焦家庄农业社视察。邓宝珊深入社员家庭嘘寒问暖,增强了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搞好春耕的勇气。就在这一年,西北局为了搞好这个试点,派干部到焦家庄指导工作,共青团西北局宣传部干部惠庶昌驻焦家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年底合作社主任房俊峰到西北局向习仲勋同志汇报工作。1954年冬,省委书记张仲良亲临焦家庄进行了视察。中共武威地委书记王俊、徐宗望,副书记张文辉更是焦家庄农业社的常客,他们经常检查工作,有时把地委常委会议也放在焦家庄召开。此外,省、地、县的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干部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己者、作家,科研单位的学者,大学教授也常到焦家庄社进行调查研究,采访报道。如作家李千峰曾到焦家庄实地考察;作家丁杰写的《高楼平地起》,使焦家庄的事迹遐迩闻名。1954年7月,甘肃省农林厅在焦家庄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国营拖拉机站,机站建立后,即在焦家庄和其它农业社签订合同进行机耕。这对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改进耕作技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年10月,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张国昌去北京参加中央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会议,并问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汇报了工作。
驻社工作组的全体干部,在建社过程中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以身作则,不搞特殊,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办好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奋力拼搏。1951冬打冰放水时,群众怀疑:“行吗?这件事前辈人可从没干过。”工作组立即进行鼓动:“人心齐,泰山移。合作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驻社干部不光是这样热情地动员组织,更重要的是亲自带头分段包干。克服“三荒”那阵,驻社干部出主意想办法,东奔西跑,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联系、求援,寻找副业生产门路,进行生产自救。办社干部吃住都和社员一样。合作社经济连年发展,公共积累不断增加,可从领导到社员,并没有忘记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方针,从不大手大脚地花集体的钱。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来的多了,外地前来参观学习的同志多了,他们坚持因陋就简地接待,把公共积累首先用于扩大再生产。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社外群众的强烈反响。开始,他们抱观望态度,经过连续两年的增产,看见焦家庄社员一改过去的贫困面貌,他们惊诧不已,于是由原来的怀疑变为羡慕,纷纷要求仿效焦家庄,组织合作社。这充分显示了典型的力量和作用。
1955年春,正当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高潮之时,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经过研究讨论,并经上级党委批准,进行了提高社的工作(即合并分红单位,牲畜折价归公等工作),将原来的生产大队改为分社,并成立了分社管理委员会。除第一分社暂时仍实行小队(原小组)分红外,二、三分社实行以社为单位分红。分社与其下属的生产耕作队签订常年包工包产合同,年终视合同完成情况进行分配。1955年12月23日,焦家庄农业社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正式转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点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刘克文执笔)
附注
①“撞田”:即根据自然墒情抢种的荒滩、荒坡上的旱地。雨水充沛的年景可获得好收成。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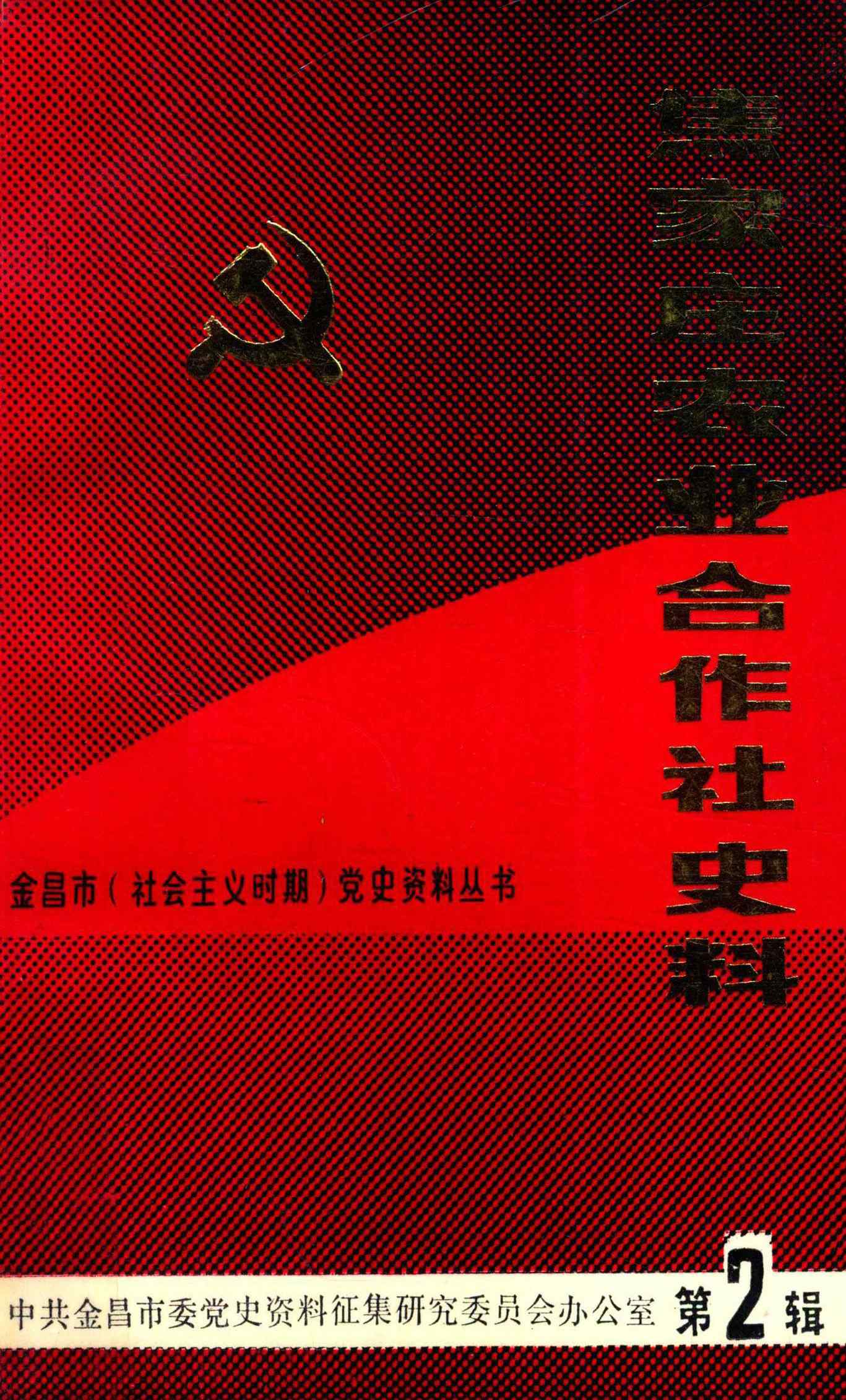
《焦家庄农业合作社史料》
本书记载和介绍的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永昌县焦家庄率先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把广大翻身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政策;把富余劳动力动员起来,因地制宜开展工副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的做法;以及按劳分配、共同致富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历程。
阅读
相关人物
刘克文
责任者
相关地名
金昌市焦家庄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