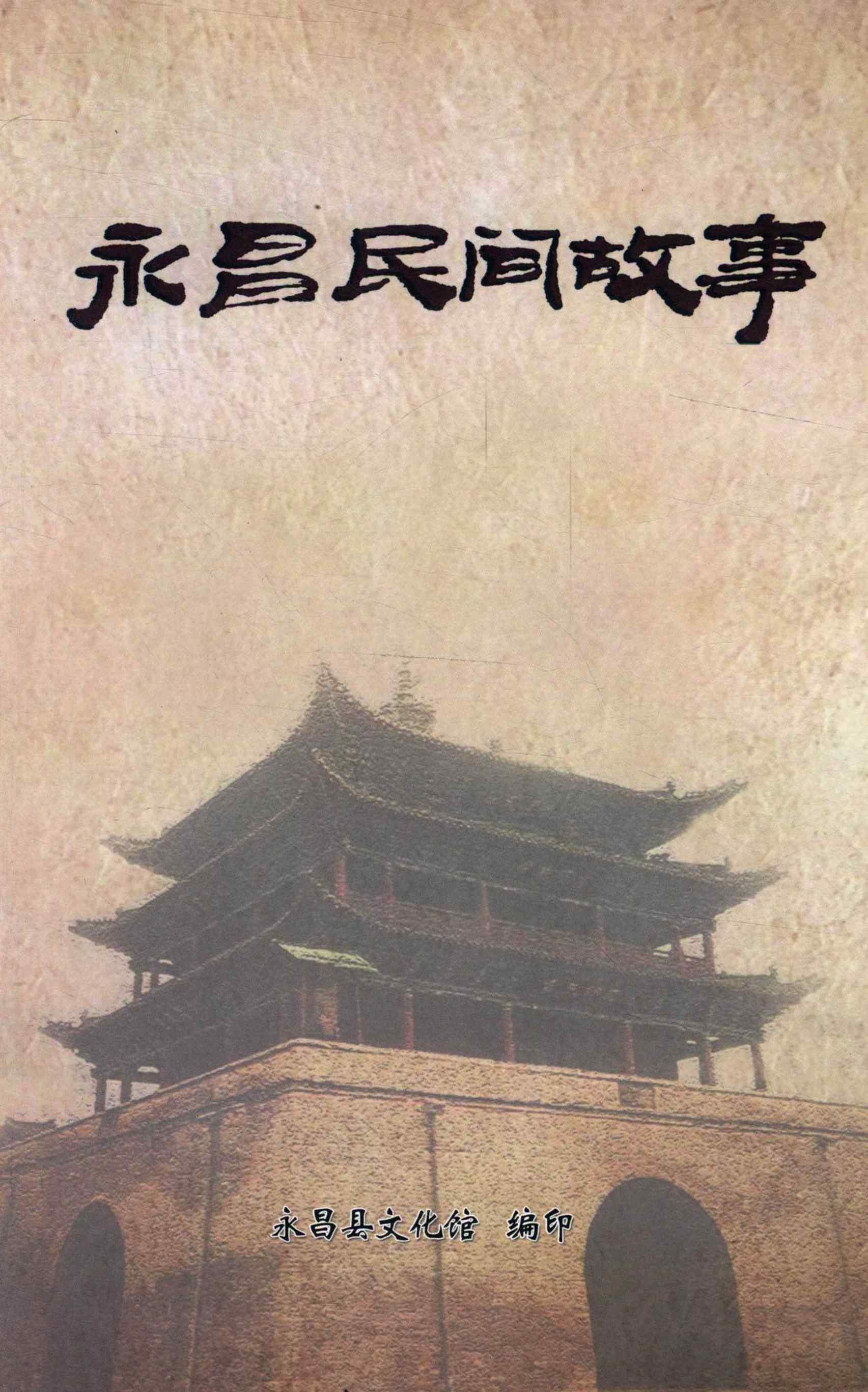内容
十五年的寻亲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海子金川西有位姓张的老先生,为了寻找失散十五年的堂姑,费尽了周折,历经了艰辛,坚持不懈地直到找见了他的堂姑。张先生的三爷爷夫妇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19岁时出闺嫁人了,这三女都是他的小三奶奶所生。不幸于1960年三位老人先后在灾荒饥饿年间饥故,撇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女儿,孤苦伶仃。那个二女叫双旋儿,7岁,三女叫跟兄儿,才3岁。张老先生面对这一双年幼堂姑的处境,实在于心不忍,义不容辞地领到家中抚养了一月有余。大队干部看到张家负担太重,就对张先生说:“你把这两个女孩子送到大队福利院去生活吧,减轻你家中的口粮负担。”张先生愉快地接受大队领导的安排,将两个年幼的堂姑,送到大队福利院。在大队福利院生活的几个月中,那年龄幼小的跟兄儿,因无亲人,哭声不断,而惹恼了保育员,对跟兄儿使用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虐待,残忍凶狠的竟将跟兄儿扣压水缸底下,骂:“你好呱喊的很了,蹲在缸底下叫唤去。”使一个失去父母的幼女心灵上忍受了灭绝人性的摧残。
1960年底,大队干部对张先生说:“大队福利院解散哩,这两个小女送到县福利院去吧,那里的生活条件要比大队的各方面都优厚的多。”对此张先生也很放心。
一挪地方,那个双旋儿不知怎么了,在县福利院死活不呆。一次,她大姐去福利院看她们,她抱住大姐的腿哭天喊地:“姐姐,我不在这里住啊!你把我领上吧,唉!……姐姐。”无奈,大姑领她来送到张先生家,张先生只好抚养着。
那年冬,县福利院给张先生捎话来,说:“跟兄儿病了,家长接回家治疗。”张先生骑驴进城去接他的小堂姑。跟兄儿身上出的水痘子,又是发高烧,张先生用大皮袄裹住抱在怀里,走到金川河边,过几根圆木拼搭的便桥,驴的一只前蹄在桥面缝隙崴了一下,前身一倾,张老猝不及防,小姑滑出皮袄,他急忙抓住肩头,险些掉到河里。一场虚惊,吓了一身冷汗,冰冷湍急的河水,一旦掉下去哪有她的活命,真是可怕极了。回到家里,张先生给他母亲说:“金川河桥上危险极了,幸亏手快抓的牢,不然,出了问题怎么给世人交待。”
小姑的病治好后,送回县福利院。1963年春末,县福利院解散时,院方竟然不通知家长,作主把小姑送了人了。送什么人了连个档案也没有,保育老师只记得是一对农村青年夫妇,口音也没记清。
张老知道把他的小姑送了人,非常的气怒:“你福利院为什么把我的人送了人?为什么不通知我领人,你们把一个人随便就送了人了?你们这么不负责任?”再吵再闹人已不知下落了,他牵肠挂肚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愧对任何人。张老的情愫深处已把他的小姑当作自己的孩子,心中暗下决心,一定在有生之年找到小姑。从六三年冬后,他利用农闲时机,走亲访友,四处托人打听小姑的下落。当时全县二十几个公社;一千多个生产队,方圆几百公里,茫茫人海,找人犹如大海捞针,实在太难了。
大约是在1977年,族中一位长辈的家中来了一位大夫,他家在清河地区,在喧谈中向他打听十几年前在县福利院被人领走的小女孩一事。那大夫说:“清河有个梅南大队毛家庄一户姓毛的人家,曾在十几年前从县福利院领养过一个小孩。”张先生从领养时间、年龄判断,这个小女孩很可能就是小姑。张先生听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被找的亲人总算是有个信息了。那年冬,张先生专程去清河梅南毛家庄找到那户人家,却得到的是冷遇。那家人死活不承认领养孩子的事,所提的要求一律拒绝,态度十分生硬。
第一次寻亲不着,败兴而归,但他心犹不甘。过了半年,张先生二下清河,没去那户毛家,而是打听到了其女婿家,才找到了他的小姑妈。张先生耐心细喧细谈,委婉地向小姑说起她三岁那年冬骑驴过桥的事,她想了一阵,才说道:“确实记得有条大河,河上有座木桥,一个穿皮袄的大人抱着骑驴过桥的,再的事印象不深,记的不清了。”此时张先生激动万分,说:“十五年来的分离,今天才算是找到我的小姑妈了,为找你确实不容易啊!”相认后又件件往事细喧给姑妈,她说都有印象。于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涌上心头,她激动地把头埋在张老的臂弯尽情号哭,张老也难控制多少年来的思念之情。他的小姑妈说:“我不想让养父母知道我见到了离散十五年的娘家人呵!”
“今天相认之后,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第三次,张先生去清河把他的小姑妈请到家来,她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和不满周岁的小女儿。
张先生十五年来寻找到他的小姑妈,在金川西传为佳话,他的为人赢得了乡亲们的好评和赞扬。第二天,张先生将跟前的两个堂姑妈妈也请来,三姐妹十五年的骨肉分离,思念情深,想认场面,激动人心。他大姑妈在庄门外的大道上,老远就忍不住大放悲声,进门就把小妹揽在怀里恸哭不已。说:“三妹啊!想死我们了。”三姐妹既悲又是喜,此时此刻她们心情难以言表。大姐的哭声嘎然而止,急切地抱过小妹的右肩,在肩胛处查验到一颗豌豆大的黑痣,验证之下,眼前的这位正是她日思夜盼的小妹妹。张先生看她们三姐妹相亲相认,缓缓地抹去泪珠,长长地舒了口气,算是了却了他心头多年来的一桩心事。
张先生的小姑妈自从那次回去后,再没来过他家。八四年、八八年张老的两个儿郎的婚事上,都去请她,答应的好好的到时要来,可不知啥原因没来,后来听人说她的大女儿在金昌化工厂工作,从此这门亲戚再没有往来过了。
(讲述人:张得智,男,55岁,永昌县文化馆馆长。)
毛寡妇要水
永昌县新城子毛家庄,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毛家庄虽是地处西大河上游,庄户人家的耕地无水灌溉,庄稼缺水,全凭的是靠天吃饭,人畜用水到西大河里挑,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西大河满河的大水从他们的村庄地边流过,可是毛家庄的农户无权引水浇灌。那时毛家庄有户姓毛的人家,这人家的主人是位寡妇,当地的人们习惯地称呼毛寡妇。这位女主人是位有主见的农家妇女,多少年来她为毛家庄缺水的事也有想法,总想着把西大河里的水要来些,给毛家庄的农户们解决农田灌溉用水的事情。她想下了一个请客求人的办法,只有摆宴席才会有希望解决水的问题,除此,再无任何良策解决这个大事情。
那位女主人召唤毛家庄所有人家的主人,集中在一起商量怎么来解决毛家庄用水的事情。问来的人谁也没有想下个更好的办法,她将自己想下的设宴求人解决的办法说给大家听,乡亲们更说这是个好办法。女主人对大家说:既然大家同意这个办法,乡亲们凑集酒席上所用东西,宴席一定摆丰盛,让客人吃喝满意才能给我们解决水的事情。那个寡妇女主人负责喊叫人们,准备酒席的东西,派得力的人去请客。她给去请客的人说,一定把客请到,凡是与西大河水有关的绅士、保长、管水的水佬都请到,专派了两位能办事的去请县长。定下的日子客人全到了,客人们吃罢酒席。县长问毛寡妇:“你设宴请我们所为何事?”毛寡妇上前跪在县长面前叩首回话:“回县太老爷的话,毛家庄的百姓,人没喝的水,地没浇的水,喝水没水,吃饭没粮,穷日子过不下去,今日设宴请县大老爷,众绅士老爷、保长、水老爷,给毛家庄的百姓解决用水的事情。”
县长听了毛寡妇的回话后,对毛寡妇说:“你收筷子去,吃了你们酒席的人用了的筷子全收来。”毛寡妇收来了酒席上的筷子,县长:“用绳子把筷子捆紧捆住,它的直径有多长,找一块磨盘石,磨盘石的中间,照筷子的直径掏一个眼,磨盘石拿去镶在分水闸口上,从磨盘石眼里出来的长流水,一年四季由毛家庄的百姓用去。”这一场酒席给毛家庄解决了这么大的大事情,那股长流水,一年四季怎么用也用不完。给下游的唐家坡、兆田的人解决了水不足的困难。有了水,毛家庄人的庄稼就好种多子,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提高。那股水一直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了南灌渠才统一到新修的干渠里。
毛寡妇身为一个农家妇女,在那个封建社会时代,出面主持毛家庄解决水的问题,确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农家妇女。没有一定的见识,没有见过世面的胆量,没有起码的才能,做成那样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当然,毛家庄周围的人们,特别是毛家庄的乡亲们尊重她是很自然的事。
(讲述人:丁生华,男,81岁,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农民。)
五女当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永昌西河某村有户人家,夫妻二人生下了九个儿女。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儿子,一群儿女,三个儿子六个姑娘。早晨天一亮吱吗子乱叫喊的,喊娘叫爹的吵闹个不休,掂尿拉屎,要吃要喝。当娘老子的忙着个手忙脚乱,顾了这个顾那个,真是有苦言不在人前。
1974年冬大女儿出嫁了,七五年给儿子娶媳成了家,二女儿三女儿都参加了集体劳动,按条件增加了劳动力,生活过得更好些。哪料想凶灾恶祸接二连三的发生在这个家,儿子是个混虫,父母面前出言伤人,对姐妹没有一点情分。为一点小事把父亲气成脑溢血,没过几天离开了人世,丢下孤儿寡母悲痛万分。儿媳妇子又好似十字坡的孙二娘,不是一般的凶恶,三天五日和婆婆吵闹,毫不留情。一次不知所为何事,喊来了娘家人大上母猪阵,立把婆婆气绝过去气死了。气死父亲的是儿子,逼死母亲的是媳妇子,一群儿女爬在母亲的身上哭爹喊娘,把娃娃们哭累堆了。“妈妈啊!你走了,我们这一群不懂事的儿女怎么活人啊?可怜我们,年幼无知如何去生存?”
二老父母,分明是他们夫妻被逼迫离人世,天不管的地不问,成了地下的冤魂。全家人本来就住着一间屋,地下躺的是母亲,炕上爬的是可怜的七个儿女。当时二女儿才17岁,最小的儿子只有3岁,母亲跌倒把二女儿吓苶了,体力弱胆又小,苶茶兮兮不知做啥好?生产队干部社员、当家户族亲戚,帮她们把母亲的后事办了。母亲葬埋后,一家七口人的担子就落在了二女儿身上,大姐大姐夫时常给安顿着说一说,也代替不了二姑娘当家的事,还得由她挣扎者去做。
二姑娘悲痛伤心地问大姐:“姐姐!妈妈这么一走,撂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叫我怎么办呢?叫我们怎么活人啊?”大姐也悲伤万分无话可给这个妹妹说:“妹妹!你坚强起来,这一家的事,只能是你来支撑着管了,我勤些来瞭望你们。”
靠父母吃饭穿衣的人,一下子要当七口人的家,这是打的鸭子上架无计无奈,千斤的担子压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怎么往起来里挑啊?看看妹妹弟弟吱吱蛤蟆的一大家子,吃吃喝喝、穿穿戴戴都不是小事情。妹妹弟弟要上学,集体的农活还得做,虽是三妹四妹也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三姐妹挣的都是低工分,挣不下工分,怎么分口粮?口粮标准低,那来的分钱的工分?有的社员骂:“我们是养活死蛤蟆烂老鼠的吗?”吃饭穿衣亮家当,啥心都得操,啥事都得做,操得不及时做得慢些都是事情。吃苦流汗是正常的事,如何把家事管好是大事情,触物生情,某一件事某种物。由不得就想起父母亲,背着妹妹弟弟们哭一场,晚上常常梦见母亲哭醒来。她是姐妹中的弱者,体力弱,智力差,患有癫痫病,情绪一激动就抽疯。当时家中相当的困难,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她当了五年的家,1980年结婚,当家的担子卸给三姑娘。
二姑娘结婚要走了,给三姑娘说:“三妹,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这些年来你帮我管这个家也有了一定经验,这个家你是会管好的。”三姑娘给二姐说:“姐姐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这个家管好的,把弟妹们关照好的。他们也一年一年的都大了,比过去好的多了,你放心吧。”
三姑娘当家的条件要比二姑当家的那几年好些了,帮二姐当家也有了些经验,家中的条件也好了一些,妹妹弟弟都大了,都上学了。自己的体力比二姐强,1981年后,农村的形势变了,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个人种的庄稼虽不如别人的好,但比往年就强多了,打下的粮食留足口粮种籽、牲口饲料外,还给国家卖议价粮一万多斤。一年来的经济大翻身,家里有钱了,冬天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车。机车买来了,可三姑娘结婚走了,四姑娘接着当这个家。那么多人的姐妹们,在前些年里那样艰难的家庭环境中,一年一年的生活过来了。四姑娘想,前些年里二姐那样的身体情况,抽疯病经常犯,家里的经济又那么差,当了五年的家。三姐走了,我就不信我当不好这个家。
出嫁了三姐,还剩三个姑娘,轮流当家轮流走,该走的时节到了就得走。四姑娘给三姐说:“三姐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这个家管好,庄稼种好,还要把两个弟弟供着考上大学,各事都要走在人前,不能让人看不起我们。”三姐说:“妹妹!你有这么好的想法打算我就放心了,我们当姐姐的常来看望你们。”
四姑娘当上家,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更好了,不仅有了手扶拖拉机车,而且盖了几间新房子。家里收拾的也好多了,吃饭有的是粮食,花钱有钱。有了机子耕地拉运打碾等,大大地减轻了人力劳动。就是姑娘家开车技术不熟练,机子开上撞到人家的庄墙上,几乎把人家的墙扛倒,碰碰磕磕地也学会使用了。这年,五妹妹初中毕业了,帮她的四姐也能干些农活和家务活了。四姑娘的三年当家,农业生产大变样,经济收入更比往年强,有什么大的事情,三个姐姐姐夫时常来往关心帮忙。两个妹妹也大了,最小的弟弟也上到高中了。
赶到五姑娘当家的三年中,大的弟弟大学毕业了,她当家到第三年,小弟弟也考上大学了。家里只有她和七妹妹了,姐姐们虽然出嫁了,但对小的妹妹关心更加亲热多了,轮到最小的妹妹当家时间也不长。五姐妹当家的十几年中,的确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十几年。五姐妹艰辛的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供出来了两名大学生,她们自己都成了家,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讲述人:蒲录林,女,58岁,红山窑乡山头庄村农民。)
持刀挡耕
故事发生在1940年前后的一件壮举之事。清河地区某村庄有户人家,那户主人李某人,他的儿子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抽大烟、耍赌博,游手好闲的浪当子。李某人教训过儿子多次,但儿子恶习总是不改。那年冬天,他没赌资,向村庄一户大地主借了十块银元,张家的掌柜问:“你借的钱用什么还哩?”其子说:“把我家的那五亩耕地顶债还给你们,”又问“你说话算数吗?”
“算数,明年春天了,你们张家耕种去。”
春种的时间,大财东家掌柜的叫长工把牛对架上犁铧耙亭,吆的骡马铁车拉的种籽,成群大阵来到李家的耕地里准备开犁播种,此时的李家主人,怀揣石头、手提铡刀去到自己的耕地上,站在地埂子上问:“你们把牲口赶到我的耕地里,想干什么?”张家的掌柜的说:“你的儿子把这五亩地抵了债,抵给我们张家了,我就得耕地啊!总不能白荒下。”
李家主人又问:“抵了什么债?我怎么不知道啊?”张家的掌柜的说:“抵了赌博债了。”李家主人说:“好啊!你们张家家大业大,势力也大,势压一方。什么事都可以做,开赌场赢钱抵押别人家的耕地,不叫别人活人。你今天成群结队,气势汹汹地来耕种我的耕地,不想活命那你们就种吧!”张家的掌柜的看李家主人手持铡刀,摆下了个拼命架势,听了李的言语后。立觉这个势头不太好,看来这块地是种不成的,立即叫长工们赶上牲口,吆上车回去了,再也不提耕种这块地的事了。
据人说那个李家的主人是一位性格耿直的汉子,为人正派,也有胆量。在那块地方上,他强人不怕,弱人不欺,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主儿。
(讲述人:徐生寿,男,76岁,水源镇赵沟村农民。)
同学相遇
黄河尚有澄清日,人岂可无有运时。某中学有位老师,他负责看学校大门。2011年某月,省人大的某秘书长,来某中学视察工作。在县、镇负责人的陪同下,正进某中学的大门时。被看大门的某人老远看见了,看见多少年难得见面的老同学,今天来到面前了非常高兴。很想出门去和老同学见一面,说句问候的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思想见不见犹豫开了。最后思之再三,机不可失,还是见一面有啥关系?他见面心切,一步迈出门房,两人见面非常亲热,握手问好又是拥抱。秘书长说:“好多年了不见,你才在这里哩,好者哩吧!”
“好者哩!”简单的两句问候话就算见了面了。
那能想到他们的见面,却给某老师惹来了麻烦,某秘书长走后,学校里的负责人批评他:“没有安排你接见,你为什么私自去接见,谁给你的权利?”某万没有想学校领导有这样的妒忌心。他受了顿窝囊气,着实的有些想不通,我和同学见了个面说了句话,又妨碍了学校的啥事了,犯了领导的啥忌?真是成了官前马后,一点不能闲扰。他对学校领导的训诉着实的想不通,晚上就给同学打了电话,说了一下今天的情况。
他在电话上说:“老同学!我们分别多少年了难得一见,实在是想你啊!今天你来学校,我见到你高兴的不得了。你走后学校领导批评我,说谁给我的权利见你,我实在有些想不通,电话上给老同学说说。”秘书长在电话上说:“你也不要生气,我们的见面正常事,我见到你很高兴……。”
老同学的友谊是很深的,秘书长一个电话打给市教育局:“某老师调市上。”市局不知那个老师在市县区的哪个学校工作,在网上查找,才找到某中学校里看大门。市局一个调令把他调到市局。一到市上,工资立增一千元。他细想了想这次和同学见面的过程,和同学的一个见面,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感谢学校领导的训斥,不是那次的训斥责问,我怎么好意思给同学打电话说我的情况?没有同学的电话,我一个看大门的职员,做梦也想不到调到市上,是我命运的大转变啊!
他与秘书长从小学到师范一直是同窗相当要好的学友,师范毕业,他分配到学校当教师,他那个同学分配乡上做文书工作。一次省上领导到乡上视察工作,乡上领导给省上领导汇报工作后,省上领导问乡领导:“你的这个汇报材料是谁写的?”乡领导指着某说:“就是这位干部写的。”省上领导回省上时间不长,就把他那个同学调省上了,自从调到省上工作就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次见面是在想念之中,是偶然的机会和同学高兴地见面。一个汇报材料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同学的一次见面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告诉人们不要小看小小的事情,和工作中的小小努力。《红楼梦》小说中,有句话是“偶因一顾,便为人上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能轻视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
(讲述人:赵兴龙,男,68岁,退休职工。)
秀才过年
解放后的新中国正是百废待新,人民群众的生活仍处在困难境况中。新政府在1950年实行减租减息,穷人的日子还是相当的艰苦。1951年的民主革命,分得的土地当年并不见效益,谁人都知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是比较长的。所以,贫穷老百姓得到了土地改革的果实,穷日子还不能马上得到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还得有个过程。那时的贫穷人家的生活转变已到了1952年的秋收以后了。
1952年春节,在水源镇赵沟村赵某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赵沟村六社,解放前叫汤赵沟生地村,村里有一户人家,老大赵增寿、老四赵景寿,原系武威县洪祥乡的人。因生地村有一户大富户人家,主人叫张浩信,是他们的亲戚,据说赵增寿、赵景寿兄弟是张浩信的亲外孙子。赵增寿定居生地村,赵增寿的父亲赵志勤是民国时期的翰林,这位老儒人也来赵沟沙沟子五神庙给赵沟的学生教书维持生活,寒暑假期间他回到洪祥老家。
1951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赵志勤的二儿子赵义寿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志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赵志勤也就成了武威县洪祥乡的一户军属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贫苦农民的生活条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基础,赵志勤这位老秀才,一样是家贫如水洗。房屋破烂,缺吃少穿,家无米面,炕无铺盖,炕洞无填的,厨下无烧的、冰炕冷灶、吃了上顿无下顿,日子过得十分寒酸。老先生过年时面对家景和自己的处境,自己亲手编写了付对联贴在了卧房门上。上联是“风来雨来时不来”,下联是“米尽面尽命不尽”,横批是“蹲着再看”。正月初一日乡政府的领导到各村给烈军属慰问拜年,洪祥乡的领导和村干部来到赵志勤家门前,一看门上贴的对联使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进门再看房屋亮麻星堂,破烂不堪;看炕上确无毡块被褥;真没有半斤八两米面;厨下无烧的,炕洞无填的。乡领导亲临其家看到了这个穷家人的境况,穷人家真有这样的穷吗?
乡政府领导立即派人到乡上取来了白面一袋,肉、菜和钱,并给拿来了一套被褥。还取得了赵志勤先生的同意,将门上的对联重新改写了一付贴上,把那付对联洗刷掉。改写的对联头条是“风调雨顺好时来”,二条改成“米有面余命运变”,横批改写上了“时来运转”。乡政府领导又对赵志勤先生说:“新政府刚成立一年过些,要办的事情太多,对你老人家的生活未及时的了解,尤其对烈军属的关心了解解决的不及时,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你还有什么要求需要解决,请你向新的人民政府提出来,政府一定帮你解决好。”
赵志勤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乡政府领导亲自到穷人家来拜年,更没有想到儿子的当兵竟能受到新政府的关怀尊重。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内心里十分感激!多半辈子生活在旧社会,备受那种贫穷苦难的穷日子,新社会给穷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讲述人:徐生寿,男,76岁,水源镇赵沟村农民。)
章祥卖猫
故事发生在1974年,农业学大寨时,县上召开了各公社书记、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会上,县上领导说:“建设大寨县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亩产四百斤上纲要,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跨长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促进大寨县建设的进展速度,加快兴修水利工程、打井抗早,农田基本建设、深翻改土、渠路林配套的条田化。今天谈一谈群众中有哪些不学大寨的具体表现,县委想听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汇报中,当时的宁远公社党委书记黄三义汇报中举例子章祥卖猫的事例。黄书记说:“章祥是个生产队长,管不住调不动的大头社员,不但不参加集体劳动,而且自由散漫。筐筐里提的猫娃子到金川大市场职工家属区卖猫,一只猫卖价十几元、二十元钱。大猫卖给人,章祥还没有回到家,猫儿早已跑回家了。第二天再将跑回的猫儿,捉住提在筐里去卖。”黄的汇报,县委领导们听得非常细心。那些年金川八八六、八冶的职工住的是平房,老鼠在职工家里泛滥成灾无法捕灭。家里的食物放不好被老鼠啃吃糟蹋,箱柜里的衣物也被老鼠咬喳损坏,所以,那时在那个地方猫儿就值钱了。这样一来章祥的卖猫行为,就成了明目张胆的对抗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事例了。
章样在那种形势下做卖猫的事情,的确是胆子够大的了。一次生产队的干部给章祥说:“你也参加队里的劳动,听说公社里知道你卖猫的事,也注意着些。”章祥答:“注意不注意,大不了把我放在群众会上批判一阵子,再他能做啥?我家里没几块钱,娃娃病下没钱给买个药,害的没有办法,谁又体谅了下我啊!我不卖猫再卖啥?”
“你哪来的那么多猫娃子去卖?”
“我养着两只大母猫儿,你是又不知道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猫儿一年产两三窝猫娃子。”
县上领导听了黄三义的汇报后,讲:“章祥卖猫不仅是不学大寨的问题,而且是脱离集体搞单干,是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的问题。公社党委要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放任自流的发展下去,以此教育群众提高阶级觉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的学大寨赶大寨,一定要把永昌县建设成为名副其实地大寨县。”
宁远公社黄书记是如何执行县上领导指示的,对章祥卖猫如何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后来再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卖猫变钱,解决家中的急需,本来是一件很小的小事,在当时形势下,却成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那时社员的一个鸡蛋卖给公卖给私,都是政治性的大问题。章祥卖猫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事,上了纲上了线就成了大事了,卖猫的名气也就大了。
(讲述人:黄三义,男,76岁,离休干部。)
违章建筑
永昌县城东北角有一大块平房,大部分住户原系县水利局职工,这块平房拆迁修建居民住宿楼。起名(永晟苑),有个姓杨的住户,是县水利局东区水泥厂工人,九十年代水泥厂停产停办,他下岗后再找不上工作。为了生存下去,无奈之下,1998年在自己住舍北墙取了个门,靠墙的外边空地上,修盖了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办了个小饭馆。饭馆面对职中学校,饭馆的生意不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没啥问题。但时间不长,城关镇、城建局、房管局、社区来干部找上门来,说他的这间小饭馆是违章建筑,不允许存在,必须拆除。
在这种情形下,夫妻二人为了全家人的生存,只能给催促拆除的干部求情下话。虽然来的干部们仍坚持拆除,但他们却回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来口头催促拆除,此后再没有来人说过拆除的事。
2009年,兰州的开发商,在永晟苑开发修楼,开发商和居民户杨家人商议拆迁的事,对他的小饭馆以违章建筑而不予补偿。杨坚持补偿,开发商就是以违章建筑,坚持不给补偿。两方未达成一致,于是开发商起诉到县法院民事庭,经判决是以“违章建筑”不予补偿。杨表示不服上诉到市中级法院民事庭判决是,维持县法院的判决,无奈之下,杨只能上兰州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杨背着申诉状和市、县法院的判决书,去兰州市找到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办公室。那里的副主任看了杨的申诉和县、市两级法院的判决后。就问杨:“你的这个小饭馆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杨回答:“一年的收入是五万多元。”那位副主任说:“你还可以经营二十年,总收入就是一百万元。”杨听了那位主任的关心问话,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赶紧回答:“经营二十多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是没啥问题的。”
信访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到金昌市中级法院民事庭:“永昌县城市居民杨成基,1998年修建的建章建筑房到今年已十一年了,违章建筑的房屋在两年内拆除不了,就成了合法的,人家一年的经营业收入五万元,再经营二十年总收入一百万元,通知开发商赔偿营业补偿费一百万元,至于房屋的拆迁补偿按规定办理。”
这堂官司,开发商找杨成基再次协商,给杨成基六十平米的门面店铺,八十平米多的框架住宅楼一套。一个人遇事的结果好坏总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加之好人主持公道才有好的结果。
(讲述人:潘锋,男,65岁,退休职工。)
张木匠惩恶
扬善上世纪三十年代,某乡陈家沟有一位技艺很高的木匠,姓张名仁义,为人正派,厌恶坏人坏事,好抱打不平,抑强扶弱,善于惩治恶人。他不但有一身木工工艺本事,而且懂星相面相、阴阳八卦,能掐会算,并有很高的武功技艺。就在同村庄有一恶霸叫胡财风,为人奸诈,横行乡里,独霸一方,欺压良善,丧尽天良。本村庄里有一位新丧偶的年轻寡妇,胡财风想强霸欺污。年轻寡妇将胡财风的行为喧说给了张木匠,木匠师傅听了年轻寡妇的喧说之后,非常气愤,心想一定要惩治一下这个胡恶霸。有一天晚上,张木匠去胡恶霸的车院里,将其铁车轱辘卸下来拿去架在了一棵大树上。第二天胡家用车时,车上的轱辘没有了,打发长工到处去找,有位长工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个啥东西在树上,到树跟前细瞅却是车轱辘架在树丫巴里了,长工赶紧去告诉给了胡财风,胡听长工诉说亲去树跟前察看,确实在树上、丫巴里架的车轱辘,但他家没有一个有本事的人能把车轱辘取下来,紧忙打发管家去请张木匠。
张木匠被请到胡家,胡财风对张木匠说:“张大师,请你来看一下,我家的车轱辘怎么架在树上了,人怎么能把车轱辘架到树上呢?”张木匠说:“能否让我看一下?”胡财风说:“就是请你张大师看一看,想啥法给我取下来。”木匠在胡财风的陪同下去一看究竟,对胡说:“这车轱辘架树上架得很奇怪,是人力无法架上去的,让我给你掐算一下是怎么回事。”张木匠掐算了一下,对胡说:“按我掐算的卦象来看,你该是对那位阴人有什么不恭的行为,做了什么失礼的事,被过路的神仙看见了,给了你个小小的惩罚,你要再不注意,将会给你带来大的灾难,到那时你后悔也已迟了。”胡恶霸听了张木匠的言说,虽不承认他的所作所为,但也有了三分的惧怕,不得不收敛他的行为。可车轱辘还在树上架着,胡问张木匠怎么将车轱辘取下来,张木匠对他说:“你只能虔诚地祭奠神灵之后,把树放倒,车轱辘就下来了。”
后来,那个胡地主要在大庄子墩上修建一间大阁楼以壮其威。胡去请张木匠把阁楼修建起来,快竣工的头两天,张木匠在阁楼上面对着下山风来的方向暗装上了一个瓷瓶子,瓶口对准来风的方向。阁楼交工后,每天早五更就听见阁楼上有种怪声,似吼声又似猫叫声,声音相当古怪难听,声音高一阵低一阵。胡家的男女老少感到非常恐怖。姓胡的赶紧打发管家去请张木匠,木匠请到家,胡把怪声一说,张说:“我给你看一下了再说?”张木匠看过之后说:“不好!胡掌柜,你这是得罪了哪路神灵了,对你家发出了警告。你干下了什么有损阴功的坏事,要你做好事、行善积德。再干了损人利己的事,将有大祸降临你家。”胡地主听了张木匠的话,吓得他六神无主,恳求张木匠很好的料理料理,答应从今往后多做善事。张木匠给胡说:“你择个好日子了,我上阁楼上去看一看究竟有什么异常事情?”胡地主择好了日子,请张木匠去看阁楼上的怪异事,张木匠在阁楼上看了一番,偷偷把那个瓷瓶顺便取下来揣到怀里,在阁楼上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下了阁楼给胡地主说:“阁楼上的神灵被我请出去了,再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再不能惹恼神灵,切记切记。”
刚立冬没几天,胡财风又打发管家请张木匠:“张大师,我家主人叫我来请你去看一下主人的上房里是啥问题?”张木匠去胡家,胡地主如接天神一般接待这位神仙,因前两次给他的事情解决的很好,总认为张木匠很可靠,也能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次请来是看他的堂屋是什么东西在作怪,胡对张木匠说:“近来上房堂屋响动的很厉害,在晚上的响声更大,家里的人不敢进堂屋的门,都很害怕,不知是啥原因?请张大师给看一下是啥东西作怪?”胡领着张木匠到上房堂屋去查看,进得堂屋门就闻着一股子老鼠气味,虽是上房堂屋,屋里的家什东西多又乱。张对胡地主说:“你上房屋里的妖气太浓,问题比较严重。究竟是什么妖精鬼怪作祟?现在实难说清楚。”胡听木匠这么说,觉着他家的事情还不是个小事情,紧忙热情招待张木匠,请张给设法把这怪事解决了。
张木匠对胡地主家里的怪事心中略有了解,还必须了解清楚是不是老鼠作怪,等把问题确实弄清了再说。他对胡地主说:“你要我解决你家里的这种怪事,必须依我的办法去做才行。”胡说:“只要能解决了那样的怪事,什么条件我都依你。”“那好!把你的这个上房屋里的东西,除米、面柜、油缸、吃的熟食外,再的东西全腾出去,再支下一张床,晚上我观察一下是什么妖魔鬼怪?然后再作道理,从明天晚上我要睡在你这个上房屋里。”张木匠回到家里画了一张阴阳八卦图,第二天拿到胡家挂在上房屋里,晚上睡在上房屋里,主意观察屋里的动静。到一更天听到米、面柜上哐啷喀喳的响声,细看是个大灰老鼠,有猫那么大,尾巴锈着个泥疙瘩,甩在米面柜上啪啪作响。观察了一晚上,基本弄清楚是老鼠在作怪,又睡者观察了两晚上,除了老鼠再无别的东西。
第四天,张木匠虚张声势诡异地给胡地主说:“你上房堂屋里的妖精比较厉害,不是我挂上那幅八卦图,我都有些怯怕,看样子是上天派来惩罚你的,从今往后再不能胡来,一定注意做好事不做坏事,行善积德。再如不注意,惹怒神灵,那就是耗财伤命的事了,你再请我是坚决不来,这次的我给你禳解着处理了。”胡地主听了张木匠的劝告后,表示从今日起坚持洗心革面多做善事,决不做坏事。张给胡又说:“今天就做,准备一条大毛毡三条麻绳,一封油饼子,三尺红布,安顿下三个伙计,必须听我指挥,三盏油灯,三辫子鞭炮,放进屋里,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上房屋,谁如进去被妖精抓住,我是无法解救。”
张木匠进上房后,将门关好点着油灯,毛毡卷成桶子,毛毡的一头用绳子捆住扎硬,把油饼子塞进毡桶里头。把油灯拨暗,坐在离毡远一些的地方细看老鼠的动静,约过了半个时辰那只大灰老鼠跑出来了,跑到毡桶口前闻了一闻就钻进毡桶里了。张木匠紧前几步一脚踏住毡桶口,用绳子捆扎住了毡桶口,又将毡桶中间捆了道绳,这就把妖怪捉住了。叫三个伙计来,两个抬毡桶,一个放鞭炮,督促伙计快步行走。一直抬往北河湾,到北河湾沿上,叫伙计放下毡桶赶紧回去,吓唬道:“处理妖精万一处理不好,抓住你们,我也无法救你们。”伙计一听没命的跑了,张木匠上去将老鼠踏死,解开绳子连毡撂到河里漂走了。这就是张仁义木匠惩恶扬善的故事。
(讲述人:国槐,男,73岁。退休教师。)
诚实兴家
相传远在明王朝洪武年间,凉州府也就是现时的武威地区的城北乡,永昌区东边有户人家,主人叫张益朋的,时年二十多岁,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张黄氏,母子二人孤儿寡母相依为生,为了生存,都在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母亲给地主家夏天薅田锄草,秋冬季节推磨碾米,打杂劳毛,挣上些米面清贫度日。母子二人虽是家境贫穷,但为人勤劳本分,从来没有非分之想,给人家做活都是以劳为实,从不投机取巧,磨奸耍滑。有一天张益朋打扫掌柜的卧室,整理书籍笔墨,擦洗桌椅,当打扫到书柜底下,放着一锭银子,张益朋将银子拾起来放进帐桌的抽屉里。张益朋的想法是单纯的,掌柜放银子时失掉在柜下了,收拾掌柜的房间应该把所有的物件放好。
掌柜的三姨太要去娘家,叫张益朋套了一辆单马小轿车吆上,把她送到娘家去。走在路上,三姨太是个很不守本分的风流女子,水性杨花,打俏卖臊,一路上再三挑逗张益朋,而张却是只顾赶车不理会三姨太的用心,毫不动点邪念,把三姨太安全的送到了她的娘家。
地主掌柜的苏谋财,家豪大富,拥有万贯家财,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名望,家中啥都富裕,唯独他已过知命之年膝下却没有儿郎,整天着实的忧愁苦闷。富豪大家而面临着断子绝后的危险,昼夜思虑,夜不成眠,日食不香,一直熬到花甲之年才接下了个秋瓜,晚年得子视如掌上明珠倍加疼爱。娃娃三,四岁时,掌柜的领的儿子去野外散心游逛,走在湖河沿边只顾观景未能留神,儿子一脚踏空失落于湖河水中。张益朋上地做活正好路过,看见少东家掉落水中,一个紧步跳进河里将少东家一把抓住抢救出来。惊呆了掌柜的,对张益朋的举动万分感激,一再表示感谢。
掌柜的苏谋财对伙计张益朋说:“你是我孩子的救命恩人,不是你机灵快速的行动,抢救下我的儿子,我将是一种什么结果啊!你是个好人!”从此以后对张另眼相看,视张益朋为救命恩人,连苏家的男夫女人都对张益朋改变了看法,都认为张益朋救了苏家的命根子。苏谋财几天来前思后想,越思越想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危险,人老了心想领上儿子游逛玩耍,哪料我眯瞪者不操心儿子掉进湖河,幸亏张益朋及时赶到,不顾一切救出了我的宝贝儿子,倘如有个闪失我怎么办呢?几天来怎么想张益朋是个好长工伙计。思虑了几天苏谋财善心萌发,无论如何要好好的感谢张益朋,如不厚礼相谢,良心上也下不去啊!一天把张益朋碰到车院里,猛想起问张益朋20几岁了,“回老爷的话28岁了。”掌柜的听说28岁的人了,年近而立之年的人尚无妻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妻子哪来儿女。出点钱财给张益朋解决婚姻之事,苏谋财为此事给管家说:“我想给张益朋说个媳妇子,你抽时间打听哪里有相仿的姑娘了,说合着把这事解决办理好。”管家听了掌柜的话也很高兴,并说:“这是主人的善心之举,定会把这事办好,”掌柜又说:“所有花费由我们开支掉,你一定把这事给办妥当办好。”
张益朋的诚实为人的举动,不仅感动了天地神灵,更感动了发财聚富的主人。张益朋的母亲听儿子说苏家掌柜的给儿子娶媳妇子,一切花费都有苏家负担,高兴着不得了,怎么感谢苏家再无别法,只有把所做的活做好。张益朋的婚事全由管家料理主办,有人给介绍来了个农家姑娘,虽不是什么美貌俊俏,但也是相貌端正,人样儿也受看,而且心地实诚的一个姑娘。婚后两年就有了身孕,五年间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七、八岁上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嵩山习武,二儿子张岳山习文,都很用功,苦学苦练。待到十八,九岁时,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大儿子张嵩山投军服役,明皇帝封大儿子为西宁镇副总兵,二儿子张岳山考取进士,封到江南的一个县的县官。这对张家来说,在那个时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母子给人家打长工的打短工的穷苦人家,一下子变成了官宦世家,这是不得了的大变化。张益朋到古稀之年后,当地民众给张家立了个孝义卫杆,张黄氏立了个贞节牌坊,以示彰扬,那个卫杆牌坊一直保留到了民国初年。
(讲述人:国槐,男,73岁,退休干部。)
抓兵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朱王堡北大沟楼庄子有两户人家,一家兄弟三人,老大在五年前抓去当兵三年后回家,另一家是兄弟二人,老二在四年前被抓去在甘州部队服兵役两年逃脱回家。1947年冬,一个黑夜里朱王堡北保的保长郭景才带领乡丁祁尚义、甲长赵千年、保丁赵某人等人。乘人睡定时间,进赵开福的庄院里,没防备的赵开福被保长、甲长、乡保丁按在睡炕上抓住用草绳背绑住拉到车院里,上衣未给穿上,精肚子上钜草绳,冷冬寒天怎么经其苦?这时躲在地窖里的老二赵开禄手提一把铡刀刃子冲出窖门直奔保长郭景才;老三赵开寿拿着一把切刀逼向带枪的乡丁祁尚义,赵万年的孙子双手举着一个石头窝子冲向保丁赵某人砸去,赵万年跑去抢住甲长赵千年的腿不放。
双方在相持中,赵开福大声喝:“把这些坏东西往死里打,打死了我去当兵抵命去。”保长郭景才在老木车上拔下一根车榔杆子抢起来打赵开禄,赵开禄也弃铡刃拔下了一根车榔杆子打郭景才。郭景才的榔杆砸空,砸在地上弹成两截子了,而赵开禄的榔杆子打在了郭景才的腿上,把郭景才的腿砸瘤了,捞着瘤腿跑出车院,其他人看见保长跑了,也都撒腿跑掉了。爷爷孙子三辈子把抓兵的人打着撵掉,解开了老大身上的绳子,穿好衣服,夜晚兄弟们再没有在屋里睡觉,躲在北大滩上的双沙窝。第二天逃往古浪县的大靖,到1949年秋永昌解放后才回到家里。
在当时旧政府把抓兵催粮催草当作头等任务,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抓兵抓壮丁应付征集兵役的任务。赵开福兄弟外逃古浪没有抓住,过了十多天的一个深夜里。保长郭景才又领乡保丁和甲长前去抓赵开敬,一阵紧促的狗吠声把赵开敬惊醒,急穿衣服忙出门,去看狗吠的是什么东西?开门刚迈出门一步,不料抓兵的已人扑到门前。保长郭景才大声下令:“还不动手等啥?”在那紧迫关头下,赵开敬立感大事不妙,急退一步到门里,顺手在门背后摸着了他准备下的铁挑钎子,一个蹦子跳在炕上,双手紧端挑钎子,大声喝道:“来吧!哪个不怕死的,就上前来动手抓来,看谁能把老子抓去?”乡丁祁尚义端着步枪对着赵开敬威胁,但赵开敬拍着胸脯说:“有本事,朝这些开枪。”赵开敬两年前被抓去,张掖驻军服过两年兵役。当过兵的人有胆量,敢于反抗。保长郭景才闯进屋里去抓人,赵开敬猛刺一挑钎子,把郭景才的皮袄捅了一个大口,吓的郭景才急忙跑出门外,再不敢进屋抓人。
那夜晚的赵开敬豁出生命勇敢反抗,乡丁不敢开枪,保甲长、保丁都不敢上前抓人,相持了两个多时辰。他们面对被抓的人,毫无办法,只得灰溜溜的离开。旧社会有句话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谁说当兵的好,爬冰卧雪谁知道。”一说当兵充军比蹲监狱还可怕,老百姓非常厌恶国民政府的强行征兵的劣行。采取各种方法来抵制反抗征兵,出家外逃的,砍掉右手食指的,到远处亲戚家躲避的,晚上不在家里睡觉的。那时代避兵是一大事情,那时的青年人一旦被抓去充军其后果结局不堪设想。四十年代初赵开有六月被抓去充军,在武威东关光明寺驻军,八月双目失明,九月部队开往绥远,失明士兵用绳拴膊牵拉到北套后病故,妻和两岁的幼儿抛在家中。
断指
一个人身上有点残疾乃是终身的痛苦,谁愿意身带残疾?这个小故事的主人把自己身体致成了残疾。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的永宁乡郑家堡有户姓张的人家,兄弟三人,上有父母在世,下有妻子儿女。家境虽然不甚富裕,生活贫淡,但还能兑凑着过得去。由于生活吃紧,战火连绵不断,兵丁徭役,苛捐杂税沉重的压在穷苦老百姓的身上,直不起腰来喘不过气来。这家兄弟三人都是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的青壮年,抓他们其中的那位当壮丁充兵役都是逃不掉的。
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代,兄弟三人采取了分奔东西,各逃兵灾,躲避兵荒。老大逃出家门到外边较远的地方打工避兵;老二领的妻子儿女外流新疆;只有老小,上离不开父母,下丢不下妻子儿女。一家人提心吊胆,惊恐不安。白天老远瞭见有三、五人前来,急忙跑出庄门去到沙堆柴湾藏下,家里的父母妻子瞭哨,等到人走远了再去柴湾喊回来。有时晚上一听狗吠声就跑出去躲避,彻夜不能睡觉,思前想后这样的躲避终究不是个头。“把这个贼娃子社会多时才活出个人来哩?”经过多少个夜晚的思虑,想出了个断指抗兵的办法,他用斧头把自己右手食指剁掉。抓兵的抓去,验兵的一看食指没有了是个废人,当兵的没有食指怎么抠扳机打枪,他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后来的日月里,乡丁保甲长再也不去抓他了。
时光流逝,艰难的熬到了1949年的秋季,1949年秋季的八九月份永昌解放了,此年的秋冬季非常的平静。在外避兵逃难的人陆续全都回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年关春节,全家人欢聚一堂,各抒情怀,都说可恶的兵荒马乱的日月过去了,今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过的。都觉着老小为了这个家,为了父母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断指成了残疾人,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可是老小却认为:“断掉指头,避掉了兵灾,照管了年迈的父母,又保全了一家人的生存,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决不后悔。”能在那个黑暗社会里,安全生存下来的穷苦人,那是相当很少的。(讲述人:王金,男,84岁,退休干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海子金川西有位姓张的老先生,为了寻找失散十五年的堂姑,费尽了周折,历经了艰辛,坚持不懈地直到找见了他的堂姑。张先生的三爷爷夫妇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19岁时出闺嫁人了,这三女都是他的小三奶奶所生。不幸于1960年三位老人先后在灾荒饥饿年间饥故,撇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女儿,孤苦伶仃。那个二女叫双旋儿,7岁,三女叫跟兄儿,才3岁。张老先生面对这一双年幼堂姑的处境,实在于心不忍,义不容辞地领到家中抚养了一月有余。大队干部看到张家负担太重,就对张先生说:“你把这两个女孩子送到大队福利院去生活吧,减轻你家中的口粮负担。”张先生愉快地接受大队领导的安排,将两个年幼的堂姑,送到大队福利院。在大队福利院生活的几个月中,那年龄幼小的跟兄儿,因无亲人,哭声不断,而惹恼了保育员,对跟兄儿使用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虐待,残忍凶狠的竟将跟兄儿扣压水缸底下,骂:“你好呱喊的很了,蹲在缸底下叫唤去。”使一个失去父母的幼女心灵上忍受了灭绝人性的摧残。
1960年底,大队干部对张先生说:“大队福利院解散哩,这两个小女送到县福利院去吧,那里的生活条件要比大队的各方面都优厚的多。”对此张先生也很放心。
一挪地方,那个双旋儿不知怎么了,在县福利院死活不呆。一次,她大姐去福利院看她们,她抱住大姐的腿哭天喊地:“姐姐,我不在这里住啊!你把我领上吧,唉!……姐姐。”无奈,大姑领她来送到张先生家,张先生只好抚养着。
那年冬,县福利院给张先生捎话来,说:“跟兄儿病了,家长接回家治疗。”张先生骑驴进城去接他的小堂姑。跟兄儿身上出的水痘子,又是发高烧,张先生用大皮袄裹住抱在怀里,走到金川河边,过几根圆木拼搭的便桥,驴的一只前蹄在桥面缝隙崴了一下,前身一倾,张老猝不及防,小姑滑出皮袄,他急忙抓住肩头,险些掉到河里。一场虚惊,吓了一身冷汗,冰冷湍急的河水,一旦掉下去哪有她的活命,真是可怕极了。回到家里,张先生给他母亲说:“金川河桥上危险极了,幸亏手快抓的牢,不然,出了问题怎么给世人交待。”
小姑的病治好后,送回县福利院。1963年春末,县福利院解散时,院方竟然不通知家长,作主把小姑送了人了。送什么人了连个档案也没有,保育老师只记得是一对农村青年夫妇,口音也没记清。
张老知道把他的小姑送了人,非常的气怒:“你福利院为什么把我的人送了人?为什么不通知我领人,你们把一个人随便就送了人了?你们这么不负责任?”再吵再闹人已不知下落了,他牵肠挂肚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愧对任何人。张老的情愫深处已把他的小姑当作自己的孩子,心中暗下决心,一定在有生之年找到小姑。从六三年冬后,他利用农闲时机,走亲访友,四处托人打听小姑的下落。当时全县二十几个公社;一千多个生产队,方圆几百公里,茫茫人海,找人犹如大海捞针,实在太难了。
大约是在1977年,族中一位长辈的家中来了一位大夫,他家在清河地区,在喧谈中向他打听十几年前在县福利院被人领走的小女孩一事。那大夫说:“清河有个梅南大队毛家庄一户姓毛的人家,曾在十几年前从县福利院领养过一个小孩。”张先生从领养时间、年龄判断,这个小女孩很可能就是小姑。张先生听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被找的亲人总算是有个信息了。那年冬,张先生专程去清河梅南毛家庄找到那户人家,却得到的是冷遇。那家人死活不承认领养孩子的事,所提的要求一律拒绝,态度十分生硬。
第一次寻亲不着,败兴而归,但他心犹不甘。过了半年,张先生二下清河,没去那户毛家,而是打听到了其女婿家,才找到了他的小姑妈。张先生耐心细喧细谈,委婉地向小姑说起她三岁那年冬骑驴过桥的事,她想了一阵,才说道:“确实记得有条大河,河上有座木桥,一个穿皮袄的大人抱着骑驴过桥的,再的事印象不深,记的不清了。”此时张先生激动万分,说:“十五年来的分离,今天才算是找到我的小姑妈了,为找你确实不容易啊!”相认后又件件往事细喧给姑妈,她说都有印象。于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涌上心头,她激动地把头埋在张老的臂弯尽情号哭,张老也难控制多少年来的思念之情。他的小姑妈说:“我不想让养父母知道我见到了离散十五年的娘家人呵!”
“今天相认之后,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第三次,张先生去清河把他的小姑妈请到家来,她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和不满周岁的小女儿。
张先生十五年来寻找到他的小姑妈,在金川西传为佳话,他的为人赢得了乡亲们的好评和赞扬。第二天,张先生将跟前的两个堂姑妈妈也请来,三姐妹十五年的骨肉分离,思念情深,想认场面,激动人心。他大姑妈在庄门外的大道上,老远就忍不住大放悲声,进门就把小妹揽在怀里恸哭不已。说:“三妹啊!想死我们了。”三姐妹既悲又是喜,此时此刻她们心情难以言表。大姐的哭声嘎然而止,急切地抱过小妹的右肩,在肩胛处查验到一颗豌豆大的黑痣,验证之下,眼前的这位正是她日思夜盼的小妹妹。张先生看她们三姐妹相亲相认,缓缓地抹去泪珠,长长地舒了口气,算是了却了他心头多年来的一桩心事。
张先生的小姑妈自从那次回去后,再没来过他家。八四年、八八年张老的两个儿郎的婚事上,都去请她,答应的好好的到时要来,可不知啥原因没来,后来听人说她的大女儿在金昌化工厂工作,从此这门亲戚再没有往来过了。
(讲述人:张得智,男,55岁,永昌县文化馆馆长。)
毛寡妇要水
永昌县新城子毛家庄,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毛家庄虽是地处西大河上游,庄户人家的耕地无水灌溉,庄稼缺水,全凭的是靠天吃饭,人畜用水到西大河里挑,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西大河满河的大水从他们的村庄地边流过,可是毛家庄的农户无权引水浇灌。那时毛家庄有户姓毛的人家,这人家的主人是位寡妇,当地的人们习惯地称呼毛寡妇。这位女主人是位有主见的农家妇女,多少年来她为毛家庄缺水的事也有想法,总想着把西大河里的水要来些,给毛家庄的农户们解决农田灌溉用水的事情。她想下了一个请客求人的办法,只有摆宴席才会有希望解决水的问题,除此,再无任何良策解决这个大事情。
那位女主人召唤毛家庄所有人家的主人,集中在一起商量怎么来解决毛家庄用水的事情。问来的人谁也没有想下个更好的办法,她将自己想下的设宴求人解决的办法说给大家听,乡亲们更说这是个好办法。女主人对大家说:既然大家同意这个办法,乡亲们凑集酒席上所用东西,宴席一定摆丰盛,让客人吃喝满意才能给我们解决水的事情。那个寡妇女主人负责喊叫人们,准备酒席的东西,派得力的人去请客。她给去请客的人说,一定把客请到,凡是与西大河水有关的绅士、保长、管水的水佬都请到,专派了两位能办事的去请县长。定下的日子客人全到了,客人们吃罢酒席。县长问毛寡妇:“你设宴请我们所为何事?”毛寡妇上前跪在县长面前叩首回话:“回县太老爷的话,毛家庄的百姓,人没喝的水,地没浇的水,喝水没水,吃饭没粮,穷日子过不下去,今日设宴请县大老爷,众绅士老爷、保长、水老爷,给毛家庄的百姓解决用水的事情。”
县长听了毛寡妇的回话后,对毛寡妇说:“你收筷子去,吃了你们酒席的人用了的筷子全收来。”毛寡妇收来了酒席上的筷子,县长:“用绳子把筷子捆紧捆住,它的直径有多长,找一块磨盘石,磨盘石的中间,照筷子的直径掏一个眼,磨盘石拿去镶在分水闸口上,从磨盘石眼里出来的长流水,一年四季由毛家庄的百姓用去。”这一场酒席给毛家庄解决了这么大的大事情,那股长流水,一年四季怎么用也用不完。给下游的唐家坡、兆田的人解决了水不足的困难。有了水,毛家庄人的庄稼就好种多子,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提高。那股水一直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了南灌渠才统一到新修的干渠里。
毛寡妇身为一个农家妇女,在那个封建社会时代,出面主持毛家庄解决水的问题,确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农家妇女。没有一定的见识,没有见过世面的胆量,没有起码的才能,做成那样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当然,毛家庄周围的人们,特别是毛家庄的乡亲们尊重她是很自然的事。
(讲述人:丁生华,男,81岁,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农民。)
五女当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永昌西河某村有户人家,夫妻二人生下了九个儿女。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儿子,一群儿女,三个儿子六个姑娘。早晨天一亮吱吗子乱叫喊的,喊娘叫爹的吵闹个不休,掂尿拉屎,要吃要喝。当娘老子的忙着个手忙脚乱,顾了这个顾那个,真是有苦言不在人前。
1974年冬大女儿出嫁了,七五年给儿子娶媳成了家,二女儿三女儿都参加了集体劳动,按条件增加了劳动力,生活过得更好些。哪料想凶灾恶祸接二连三的发生在这个家,儿子是个混虫,父母面前出言伤人,对姐妹没有一点情分。为一点小事把父亲气成脑溢血,没过几天离开了人世,丢下孤儿寡母悲痛万分。儿媳妇子又好似十字坡的孙二娘,不是一般的凶恶,三天五日和婆婆吵闹,毫不留情。一次不知所为何事,喊来了娘家人大上母猪阵,立把婆婆气绝过去气死了。气死父亲的是儿子,逼死母亲的是媳妇子,一群儿女爬在母亲的身上哭爹喊娘,把娃娃们哭累堆了。“妈妈啊!你走了,我们这一群不懂事的儿女怎么活人啊?可怜我们,年幼无知如何去生存?”
二老父母,分明是他们夫妻被逼迫离人世,天不管的地不问,成了地下的冤魂。全家人本来就住着一间屋,地下躺的是母亲,炕上爬的是可怜的七个儿女。当时二女儿才17岁,最小的儿子只有3岁,母亲跌倒把二女儿吓苶了,体力弱胆又小,苶茶兮兮不知做啥好?生产队干部社员、当家户族亲戚,帮她们把母亲的后事办了。母亲葬埋后,一家七口人的担子就落在了二女儿身上,大姐大姐夫时常给安顿着说一说,也代替不了二姑娘当家的事,还得由她挣扎者去做。
二姑娘悲痛伤心地问大姐:“姐姐!妈妈这么一走,撂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叫我怎么办呢?叫我们怎么活人啊?”大姐也悲伤万分无话可给这个妹妹说:“妹妹!你坚强起来,这一家的事,只能是你来支撑着管了,我勤些来瞭望你们。”
靠父母吃饭穿衣的人,一下子要当七口人的家,这是打的鸭子上架无计无奈,千斤的担子压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怎么往起来里挑啊?看看妹妹弟弟吱吱蛤蟆的一大家子,吃吃喝喝、穿穿戴戴都不是小事情。妹妹弟弟要上学,集体的农活还得做,虽是三妹四妹也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三姐妹挣的都是低工分,挣不下工分,怎么分口粮?口粮标准低,那来的分钱的工分?有的社员骂:“我们是养活死蛤蟆烂老鼠的吗?”吃饭穿衣亮家当,啥心都得操,啥事都得做,操得不及时做得慢些都是事情。吃苦流汗是正常的事,如何把家事管好是大事情,触物生情,某一件事某种物。由不得就想起父母亲,背着妹妹弟弟们哭一场,晚上常常梦见母亲哭醒来。她是姐妹中的弱者,体力弱,智力差,患有癫痫病,情绪一激动就抽疯。当时家中相当的困难,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她当了五年的家,1980年结婚,当家的担子卸给三姑娘。
二姑娘结婚要走了,给三姑娘说:“三妹,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这些年来你帮我管这个家也有了一定经验,这个家你是会管好的。”三姑娘给二姐说:“姐姐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这个家管好的,把弟妹们关照好的。他们也一年一年的都大了,比过去好的多了,你放心吧。”
三姑娘当家的条件要比二姑当家的那几年好些了,帮二姐当家也有了些经验,家中的条件也好了一些,妹妹弟弟都大了,都上学了。自己的体力比二姐强,1981年后,农村的形势变了,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个人种的庄稼虽不如别人的好,但比往年就强多了,打下的粮食留足口粮种籽、牲口饲料外,还给国家卖议价粮一万多斤。一年来的经济大翻身,家里有钱了,冬天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车。机车买来了,可三姑娘结婚走了,四姑娘接着当这个家。那么多人的姐妹们,在前些年里那样艰难的家庭环境中,一年一年的生活过来了。四姑娘想,前些年里二姐那样的身体情况,抽疯病经常犯,家里的经济又那么差,当了五年的家。三姐走了,我就不信我当不好这个家。
出嫁了三姐,还剩三个姑娘,轮流当家轮流走,该走的时节到了就得走。四姑娘给三姐说:“三姐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这个家管好,庄稼种好,还要把两个弟弟供着考上大学,各事都要走在人前,不能让人看不起我们。”三姐说:“妹妹!你有这么好的想法打算我就放心了,我们当姐姐的常来看望你们。”
四姑娘当上家,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更好了,不仅有了手扶拖拉机车,而且盖了几间新房子。家里收拾的也好多了,吃饭有的是粮食,花钱有钱。有了机子耕地拉运打碾等,大大地减轻了人力劳动。就是姑娘家开车技术不熟练,机子开上撞到人家的庄墙上,几乎把人家的墙扛倒,碰碰磕磕地也学会使用了。这年,五妹妹初中毕业了,帮她的四姐也能干些农活和家务活了。四姑娘的三年当家,农业生产大变样,经济收入更比往年强,有什么大的事情,三个姐姐姐夫时常来往关心帮忙。两个妹妹也大了,最小的弟弟也上到高中了。
赶到五姑娘当家的三年中,大的弟弟大学毕业了,她当家到第三年,小弟弟也考上大学了。家里只有她和七妹妹了,姐姐们虽然出嫁了,但对小的妹妹关心更加亲热多了,轮到最小的妹妹当家时间也不长。五姐妹当家的十几年中,的确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十几年。五姐妹艰辛的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供出来了两名大学生,她们自己都成了家,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讲述人:蒲录林,女,58岁,红山窑乡山头庄村农民。)
持刀挡耕
故事发生在1940年前后的一件壮举之事。清河地区某村庄有户人家,那户主人李某人,他的儿子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抽大烟、耍赌博,游手好闲的浪当子。李某人教训过儿子多次,但儿子恶习总是不改。那年冬天,他没赌资,向村庄一户大地主借了十块银元,张家的掌柜问:“你借的钱用什么还哩?”其子说:“把我家的那五亩耕地顶债还给你们,”又问“你说话算数吗?”
“算数,明年春天了,你们张家耕种去。”
春种的时间,大财东家掌柜的叫长工把牛对架上犁铧耙亭,吆的骡马铁车拉的种籽,成群大阵来到李家的耕地里准备开犁播种,此时的李家主人,怀揣石头、手提铡刀去到自己的耕地上,站在地埂子上问:“你们把牲口赶到我的耕地里,想干什么?”张家的掌柜的说:“你的儿子把这五亩地抵了债,抵给我们张家了,我就得耕地啊!总不能白荒下。”
李家主人又问:“抵了什么债?我怎么不知道啊?”张家的掌柜的说:“抵了赌博债了。”李家主人说:“好啊!你们张家家大业大,势力也大,势压一方。什么事都可以做,开赌场赢钱抵押别人家的耕地,不叫别人活人。你今天成群结队,气势汹汹地来耕种我的耕地,不想活命那你们就种吧!”张家的掌柜的看李家主人手持铡刀,摆下了个拼命架势,听了李的言语后。立觉这个势头不太好,看来这块地是种不成的,立即叫长工们赶上牲口,吆上车回去了,再也不提耕种这块地的事了。
据人说那个李家的主人是一位性格耿直的汉子,为人正派,也有胆量。在那块地方上,他强人不怕,弱人不欺,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主儿。
(讲述人:徐生寿,男,76岁,水源镇赵沟村农民。)
同学相遇
黄河尚有澄清日,人岂可无有运时。某中学有位老师,他负责看学校大门。2011年某月,省人大的某秘书长,来某中学视察工作。在县、镇负责人的陪同下,正进某中学的大门时。被看大门的某人老远看见了,看见多少年难得见面的老同学,今天来到面前了非常高兴。很想出门去和老同学见一面,说句问候的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思想见不见犹豫开了。最后思之再三,机不可失,还是见一面有啥关系?他见面心切,一步迈出门房,两人见面非常亲热,握手问好又是拥抱。秘书长说:“好多年了不见,你才在这里哩,好者哩吧!”
“好者哩!”简单的两句问候话就算见了面了。
那能想到他们的见面,却给某老师惹来了麻烦,某秘书长走后,学校里的负责人批评他:“没有安排你接见,你为什么私自去接见,谁给你的权利?”某万没有想学校领导有这样的妒忌心。他受了顿窝囊气,着实的有些想不通,我和同学见了个面说了句话,又妨碍了学校的啥事了,犯了领导的啥忌?真是成了官前马后,一点不能闲扰。他对学校领导的训诉着实的想不通,晚上就给同学打了电话,说了一下今天的情况。
他在电话上说:“老同学!我们分别多少年了难得一见,实在是想你啊!今天你来学校,我见到你高兴的不得了。你走后学校领导批评我,说谁给我的权利见你,我实在有些想不通,电话上给老同学说说。”秘书长在电话上说:“你也不要生气,我们的见面正常事,我见到你很高兴……。”
老同学的友谊是很深的,秘书长一个电话打给市教育局:“某老师调市上。”市局不知那个老师在市县区的哪个学校工作,在网上查找,才找到某中学校里看大门。市局一个调令把他调到市局。一到市上,工资立增一千元。他细想了想这次和同学见面的过程,和同学的一个见面,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感谢学校领导的训斥,不是那次的训斥责问,我怎么好意思给同学打电话说我的情况?没有同学的电话,我一个看大门的职员,做梦也想不到调到市上,是我命运的大转变啊!
他与秘书长从小学到师范一直是同窗相当要好的学友,师范毕业,他分配到学校当教师,他那个同学分配乡上做文书工作。一次省上领导到乡上视察工作,乡上领导给省上领导汇报工作后,省上领导问乡领导:“你的这个汇报材料是谁写的?”乡领导指着某说:“就是这位干部写的。”省上领导回省上时间不长,就把他那个同学调省上了,自从调到省上工作就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次见面是在想念之中,是偶然的机会和同学高兴地见面。一个汇报材料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同学的一次见面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告诉人们不要小看小小的事情,和工作中的小小努力。《红楼梦》小说中,有句话是“偶因一顾,便为人上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能轻视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
(讲述人:赵兴龙,男,68岁,退休职工。)
秀才过年
解放后的新中国正是百废待新,人民群众的生活仍处在困难境况中。新政府在1950年实行减租减息,穷人的日子还是相当的艰苦。1951年的民主革命,分得的土地当年并不见效益,谁人都知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是比较长的。所以,贫穷老百姓得到了土地改革的果实,穷日子还不能马上得到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还得有个过程。那时的贫穷人家的生活转变已到了1952年的秋收以后了。
1952年春节,在水源镇赵沟村赵某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赵沟村六社,解放前叫汤赵沟生地村,村里有一户人家,老大赵增寿、老四赵景寿,原系武威县洪祥乡的人。因生地村有一户大富户人家,主人叫张浩信,是他们的亲戚,据说赵增寿、赵景寿兄弟是张浩信的亲外孙子。赵增寿定居生地村,赵增寿的父亲赵志勤是民国时期的翰林,这位老儒人也来赵沟沙沟子五神庙给赵沟的学生教书维持生活,寒暑假期间他回到洪祥老家。
1951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赵志勤的二儿子赵义寿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志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赵志勤也就成了武威县洪祥乡的一户军属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贫苦农民的生活条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基础,赵志勤这位老秀才,一样是家贫如水洗。房屋破烂,缺吃少穿,家无米面,炕无铺盖,炕洞无填的,厨下无烧的、冰炕冷灶、吃了上顿无下顿,日子过得十分寒酸。老先生过年时面对家景和自己的处境,自己亲手编写了付对联贴在了卧房门上。上联是“风来雨来时不来”,下联是“米尽面尽命不尽”,横批是“蹲着再看”。正月初一日乡政府的领导到各村给烈军属慰问拜年,洪祥乡的领导和村干部来到赵志勤家门前,一看门上贴的对联使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进门再看房屋亮麻星堂,破烂不堪;看炕上确无毡块被褥;真没有半斤八两米面;厨下无烧的,炕洞无填的。乡领导亲临其家看到了这个穷家人的境况,穷人家真有这样的穷吗?
乡政府领导立即派人到乡上取来了白面一袋,肉、菜和钱,并给拿来了一套被褥。还取得了赵志勤先生的同意,将门上的对联重新改写了一付贴上,把那付对联洗刷掉。改写的对联头条是“风调雨顺好时来”,二条改成“米有面余命运变”,横批改写上了“时来运转”。乡政府领导又对赵志勤先生说:“新政府刚成立一年过些,要办的事情太多,对你老人家的生活未及时的了解,尤其对烈军属的关心了解解决的不及时,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你还有什么要求需要解决,请你向新的人民政府提出来,政府一定帮你解决好。”
赵志勤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乡政府领导亲自到穷人家来拜年,更没有想到儿子的当兵竟能受到新政府的关怀尊重。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内心里十分感激!多半辈子生活在旧社会,备受那种贫穷苦难的穷日子,新社会给穷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讲述人:徐生寿,男,76岁,水源镇赵沟村农民。)
章祥卖猫
故事发生在1974年,农业学大寨时,县上召开了各公社书记、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会上,县上领导说:“建设大寨县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亩产四百斤上纲要,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跨长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促进大寨县建设的进展速度,加快兴修水利工程、打井抗早,农田基本建设、深翻改土、渠路林配套的条田化。今天谈一谈群众中有哪些不学大寨的具体表现,县委想听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汇报中,当时的宁远公社党委书记黄三义汇报中举例子章祥卖猫的事例。黄书记说:“章祥是个生产队长,管不住调不动的大头社员,不但不参加集体劳动,而且自由散漫。筐筐里提的猫娃子到金川大市场职工家属区卖猫,一只猫卖价十几元、二十元钱。大猫卖给人,章祥还没有回到家,猫儿早已跑回家了。第二天再将跑回的猫儿,捉住提在筐里去卖。”黄的汇报,县委领导们听得非常细心。那些年金川八八六、八冶的职工住的是平房,老鼠在职工家里泛滥成灾无法捕灭。家里的食物放不好被老鼠啃吃糟蹋,箱柜里的衣物也被老鼠咬喳损坏,所以,那时在那个地方猫儿就值钱了。这样一来章祥的卖猫行为,就成了明目张胆的对抗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事例了。
章样在那种形势下做卖猫的事情,的确是胆子够大的了。一次生产队的干部给章祥说:“你也参加队里的劳动,听说公社里知道你卖猫的事,也注意着些。”章祥答:“注意不注意,大不了把我放在群众会上批判一阵子,再他能做啥?我家里没几块钱,娃娃病下没钱给买个药,害的没有办法,谁又体谅了下我啊!我不卖猫再卖啥?”
“你哪来的那么多猫娃子去卖?”
“我养着两只大母猫儿,你是又不知道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猫儿一年产两三窝猫娃子。”
县上领导听了黄三义的汇报后,讲:“章祥卖猫不仅是不学大寨的问题,而且是脱离集体搞单干,是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的问题。公社党委要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放任自流的发展下去,以此教育群众提高阶级觉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的学大寨赶大寨,一定要把永昌县建设成为名副其实地大寨县。”
宁远公社黄书记是如何执行县上领导指示的,对章祥卖猫如何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后来再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卖猫变钱,解决家中的急需,本来是一件很小的小事,在当时形势下,却成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那时社员的一个鸡蛋卖给公卖给私,都是政治性的大问题。章祥卖猫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事,上了纲上了线就成了大事了,卖猫的名气也就大了。
(讲述人:黄三义,男,76岁,离休干部。)
违章建筑
永昌县城东北角有一大块平房,大部分住户原系县水利局职工,这块平房拆迁修建居民住宿楼。起名(永晟苑),有个姓杨的住户,是县水利局东区水泥厂工人,九十年代水泥厂停产停办,他下岗后再找不上工作。为了生存下去,无奈之下,1998年在自己住舍北墙取了个门,靠墙的外边空地上,修盖了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办了个小饭馆。饭馆面对职中学校,饭馆的生意不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没啥问题。但时间不长,城关镇、城建局、房管局、社区来干部找上门来,说他的这间小饭馆是违章建筑,不允许存在,必须拆除。
在这种情形下,夫妻二人为了全家人的生存,只能给催促拆除的干部求情下话。虽然来的干部们仍坚持拆除,但他们却回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来口头催促拆除,此后再没有来人说过拆除的事。
2009年,兰州的开发商,在永晟苑开发修楼,开发商和居民户杨家人商议拆迁的事,对他的小饭馆以违章建筑而不予补偿。杨坚持补偿,开发商就是以违章建筑,坚持不给补偿。两方未达成一致,于是开发商起诉到县法院民事庭,经判决是以“违章建筑”不予补偿。杨表示不服上诉到市中级法院民事庭判决是,维持县法院的判决,无奈之下,杨只能上兰州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杨背着申诉状和市、县法院的判决书,去兰州市找到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办公室。那里的副主任看了杨的申诉和县、市两级法院的判决后。就问杨:“你的这个小饭馆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杨回答:“一年的收入是五万多元。”那位副主任说:“你还可以经营二十年,总收入就是一百万元。”杨听了那位主任的关心问话,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赶紧回答:“经营二十多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是没啥问题的。”
信访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到金昌市中级法院民事庭:“永昌县城市居民杨成基,1998年修建的建章建筑房到今年已十一年了,违章建筑的房屋在两年内拆除不了,就成了合法的,人家一年的经营业收入五万元,再经营二十年总收入一百万元,通知开发商赔偿营业补偿费一百万元,至于房屋的拆迁补偿按规定办理。”
这堂官司,开发商找杨成基再次协商,给杨成基六十平米的门面店铺,八十平米多的框架住宅楼一套。一个人遇事的结果好坏总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加之好人主持公道才有好的结果。
(讲述人:潘锋,男,65岁,退休职工。)
张木匠惩恶
扬善上世纪三十年代,某乡陈家沟有一位技艺很高的木匠,姓张名仁义,为人正派,厌恶坏人坏事,好抱打不平,抑强扶弱,善于惩治恶人。他不但有一身木工工艺本事,而且懂星相面相、阴阳八卦,能掐会算,并有很高的武功技艺。就在同村庄有一恶霸叫胡财风,为人奸诈,横行乡里,独霸一方,欺压良善,丧尽天良。本村庄里有一位新丧偶的年轻寡妇,胡财风想强霸欺污。年轻寡妇将胡财风的行为喧说给了张木匠,木匠师傅听了年轻寡妇的喧说之后,非常气愤,心想一定要惩治一下这个胡恶霸。有一天晚上,张木匠去胡恶霸的车院里,将其铁车轱辘卸下来拿去架在了一棵大树上。第二天胡家用车时,车上的轱辘没有了,打发长工到处去找,有位长工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个啥东西在树上,到树跟前细瞅却是车轱辘架在树丫巴里了,长工赶紧去告诉给了胡财风,胡听长工诉说亲去树跟前察看,确实在树上、丫巴里架的车轱辘,但他家没有一个有本事的人能把车轱辘取下来,紧忙打发管家去请张木匠。
张木匠被请到胡家,胡财风对张木匠说:“张大师,请你来看一下,我家的车轱辘怎么架在树上了,人怎么能把车轱辘架到树上呢?”张木匠说:“能否让我看一下?”胡财风说:“就是请你张大师看一看,想啥法给我取下来。”木匠在胡财风的陪同下去一看究竟,对胡说:“这车轱辘架树上架得很奇怪,是人力无法架上去的,让我给你掐算一下是怎么回事。”张木匠掐算了一下,对胡说:“按我掐算的卦象来看,你该是对那位阴人有什么不恭的行为,做了什么失礼的事,被过路的神仙看见了,给了你个小小的惩罚,你要再不注意,将会给你带来大的灾难,到那时你后悔也已迟了。”胡恶霸听了张木匠的言说,虽不承认他的所作所为,但也有了三分的惧怕,不得不收敛他的行为。可车轱辘还在树上架着,胡问张木匠怎么将车轱辘取下来,张木匠对他说:“你只能虔诚地祭奠神灵之后,把树放倒,车轱辘就下来了。”
后来,那个胡地主要在大庄子墩上修建一间大阁楼以壮其威。胡去请张木匠把阁楼修建起来,快竣工的头两天,张木匠在阁楼上面对着下山风来的方向暗装上了一个瓷瓶子,瓶口对准来风的方向。阁楼交工后,每天早五更就听见阁楼上有种怪声,似吼声又似猫叫声,声音相当古怪难听,声音高一阵低一阵。胡家的男女老少感到非常恐怖。姓胡的赶紧打发管家去请张木匠,木匠请到家,胡把怪声一说,张说:“我给你看一下了再说?”张木匠看过之后说:“不好!胡掌柜,你这是得罪了哪路神灵了,对你家发出了警告。你干下了什么有损阴功的坏事,要你做好事、行善积德。再干了损人利己的事,将有大祸降临你家。”胡地主听了张木匠的话,吓得他六神无主,恳求张木匠很好的料理料理,答应从今往后多做善事。张木匠给胡说:“你择个好日子了,我上阁楼上去看一看究竟有什么异常事情?”胡地主择好了日子,请张木匠去看阁楼上的怪异事,张木匠在阁楼上看了一番,偷偷把那个瓷瓶顺便取下来揣到怀里,在阁楼上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下了阁楼给胡地主说:“阁楼上的神灵被我请出去了,再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再不能惹恼神灵,切记切记。”
刚立冬没几天,胡财风又打发管家请张木匠:“张大师,我家主人叫我来请你去看一下主人的上房里是啥问题?”张木匠去胡家,胡地主如接天神一般接待这位神仙,因前两次给他的事情解决的很好,总认为张木匠很可靠,也能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次请来是看他的堂屋是什么东西在作怪,胡对张木匠说:“近来上房堂屋响动的很厉害,在晚上的响声更大,家里的人不敢进堂屋的门,都很害怕,不知是啥原因?请张大师给看一下是啥东西作怪?”胡领着张木匠到上房堂屋去查看,进得堂屋门就闻着一股子老鼠气味,虽是上房堂屋,屋里的家什东西多又乱。张对胡地主说:“你上房屋里的妖气太浓,问题比较严重。究竟是什么妖精鬼怪作祟?现在实难说清楚。”胡听木匠这么说,觉着他家的事情还不是个小事情,紧忙热情招待张木匠,请张给设法把这怪事解决了。
张木匠对胡地主家里的怪事心中略有了解,还必须了解清楚是不是老鼠作怪,等把问题确实弄清了再说。他对胡地主说:“你要我解决你家里的这种怪事,必须依我的办法去做才行。”胡说:“只要能解决了那样的怪事,什么条件我都依你。”“那好!把你的这个上房屋里的东西,除米、面柜、油缸、吃的熟食外,再的东西全腾出去,再支下一张床,晚上我观察一下是什么妖魔鬼怪?然后再作道理,从明天晚上我要睡在你这个上房屋里。”张木匠回到家里画了一张阴阳八卦图,第二天拿到胡家挂在上房屋里,晚上睡在上房屋里,主意观察屋里的动静。到一更天听到米、面柜上哐啷喀喳的响声,细看是个大灰老鼠,有猫那么大,尾巴锈着个泥疙瘩,甩在米面柜上啪啪作响。观察了一晚上,基本弄清楚是老鼠在作怪,又睡者观察了两晚上,除了老鼠再无别的东西。
第四天,张木匠虚张声势诡异地给胡地主说:“你上房堂屋里的妖精比较厉害,不是我挂上那幅八卦图,我都有些怯怕,看样子是上天派来惩罚你的,从今往后再不能胡来,一定注意做好事不做坏事,行善积德。再如不注意,惹怒神灵,那就是耗财伤命的事了,你再请我是坚决不来,这次的我给你禳解着处理了。”胡地主听了张木匠的劝告后,表示从今日起坚持洗心革面多做善事,决不做坏事。张给胡又说:“今天就做,准备一条大毛毡三条麻绳,一封油饼子,三尺红布,安顿下三个伙计,必须听我指挥,三盏油灯,三辫子鞭炮,放进屋里,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上房屋,谁如进去被妖精抓住,我是无法解救。”
张木匠进上房后,将门关好点着油灯,毛毡卷成桶子,毛毡的一头用绳子捆住扎硬,把油饼子塞进毡桶里头。把油灯拨暗,坐在离毡远一些的地方细看老鼠的动静,约过了半个时辰那只大灰老鼠跑出来了,跑到毡桶口前闻了一闻就钻进毡桶里了。张木匠紧前几步一脚踏住毡桶口,用绳子捆扎住了毡桶口,又将毡桶中间捆了道绳,这就把妖怪捉住了。叫三个伙计来,两个抬毡桶,一个放鞭炮,督促伙计快步行走。一直抬往北河湾,到北河湾沿上,叫伙计放下毡桶赶紧回去,吓唬道:“处理妖精万一处理不好,抓住你们,我也无法救你们。”伙计一听没命的跑了,张木匠上去将老鼠踏死,解开绳子连毡撂到河里漂走了。这就是张仁义木匠惩恶扬善的故事。
(讲述人:国槐,男,73岁。退休教师。)
诚实兴家
相传远在明王朝洪武年间,凉州府也就是现时的武威地区的城北乡,永昌区东边有户人家,主人叫张益朋的,时年二十多岁,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张黄氏,母子二人孤儿寡母相依为生,为了生存,都在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母亲给地主家夏天薅田锄草,秋冬季节推磨碾米,打杂劳毛,挣上些米面清贫度日。母子二人虽是家境贫穷,但为人勤劳本分,从来没有非分之想,给人家做活都是以劳为实,从不投机取巧,磨奸耍滑。有一天张益朋打扫掌柜的卧室,整理书籍笔墨,擦洗桌椅,当打扫到书柜底下,放着一锭银子,张益朋将银子拾起来放进帐桌的抽屉里。张益朋的想法是单纯的,掌柜放银子时失掉在柜下了,收拾掌柜的房间应该把所有的物件放好。
掌柜的三姨太要去娘家,叫张益朋套了一辆单马小轿车吆上,把她送到娘家去。走在路上,三姨太是个很不守本分的风流女子,水性杨花,打俏卖臊,一路上再三挑逗张益朋,而张却是只顾赶车不理会三姨太的用心,毫不动点邪念,把三姨太安全的送到了她的娘家。
地主掌柜的苏谋财,家豪大富,拥有万贯家财,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名望,家中啥都富裕,唯独他已过知命之年膝下却没有儿郎,整天着实的忧愁苦闷。富豪大家而面临着断子绝后的危险,昼夜思虑,夜不成眠,日食不香,一直熬到花甲之年才接下了个秋瓜,晚年得子视如掌上明珠倍加疼爱。娃娃三,四岁时,掌柜的领的儿子去野外散心游逛,走在湖河沿边只顾观景未能留神,儿子一脚踏空失落于湖河水中。张益朋上地做活正好路过,看见少东家掉落水中,一个紧步跳进河里将少东家一把抓住抢救出来。惊呆了掌柜的,对张益朋的举动万分感激,一再表示感谢。
掌柜的苏谋财对伙计张益朋说:“你是我孩子的救命恩人,不是你机灵快速的行动,抢救下我的儿子,我将是一种什么结果啊!你是个好人!”从此以后对张另眼相看,视张益朋为救命恩人,连苏家的男夫女人都对张益朋改变了看法,都认为张益朋救了苏家的命根子。苏谋财几天来前思后想,越思越想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危险,人老了心想领上儿子游逛玩耍,哪料我眯瞪者不操心儿子掉进湖河,幸亏张益朋及时赶到,不顾一切救出了我的宝贝儿子,倘如有个闪失我怎么办呢?几天来怎么想张益朋是个好长工伙计。思虑了几天苏谋财善心萌发,无论如何要好好的感谢张益朋,如不厚礼相谢,良心上也下不去啊!一天把张益朋碰到车院里,猛想起问张益朋20几岁了,“回老爷的话28岁了。”掌柜的听说28岁的人了,年近而立之年的人尚无妻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妻子哪来儿女。出点钱财给张益朋解决婚姻之事,苏谋财为此事给管家说:“我想给张益朋说个媳妇子,你抽时间打听哪里有相仿的姑娘了,说合着把这事解决办理好。”管家听了掌柜的话也很高兴,并说:“这是主人的善心之举,定会把这事办好,”掌柜又说:“所有花费由我们开支掉,你一定把这事给办妥当办好。”
张益朋的诚实为人的举动,不仅感动了天地神灵,更感动了发财聚富的主人。张益朋的母亲听儿子说苏家掌柜的给儿子娶媳妇子,一切花费都有苏家负担,高兴着不得了,怎么感谢苏家再无别法,只有把所做的活做好。张益朋的婚事全由管家料理主办,有人给介绍来了个农家姑娘,虽不是什么美貌俊俏,但也是相貌端正,人样儿也受看,而且心地实诚的一个姑娘。婚后两年就有了身孕,五年间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七、八岁上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嵩山习武,二儿子张岳山习文,都很用功,苦学苦练。待到十八,九岁时,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大儿子张嵩山投军服役,明皇帝封大儿子为西宁镇副总兵,二儿子张岳山考取进士,封到江南的一个县的县官。这对张家来说,在那个时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母子给人家打长工的打短工的穷苦人家,一下子变成了官宦世家,这是不得了的大变化。张益朋到古稀之年后,当地民众给张家立了个孝义卫杆,张黄氏立了个贞节牌坊,以示彰扬,那个卫杆牌坊一直保留到了民国初年。
(讲述人:国槐,男,73岁,退休干部。)
抓兵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朱王堡北大沟楼庄子有两户人家,一家兄弟三人,老大在五年前抓去当兵三年后回家,另一家是兄弟二人,老二在四年前被抓去在甘州部队服兵役两年逃脱回家。1947年冬,一个黑夜里朱王堡北保的保长郭景才带领乡丁祁尚义、甲长赵千年、保丁赵某人等人。乘人睡定时间,进赵开福的庄院里,没防备的赵开福被保长、甲长、乡保丁按在睡炕上抓住用草绳背绑住拉到车院里,上衣未给穿上,精肚子上钜草绳,冷冬寒天怎么经其苦?这时躲在地窖里的老二赵开禄手提一把铡刀刃子冲出窖门直奔保长郭景才;老三赵开寿拿着一把切刀逼向带枪的乡丁祁尚义,赵万年的孙子双手举着一个石头窝子冲向保丁赵某人砸去,赵万年跑去抢住甲长赵千年的腿不放。
双方在相持中,赵开福大声喝:“把这些坏东西往死里打,打死了我去当兵抵命去。”保长郭景才在老木车上拔下一根车榔杆子抢起来打赵开禄,赵开禄也弃铡刃拔下了一根车榔杆子打郭景才。郭景才的榔杆砸空,砸在地上弹成两截子了,而赵开禄的榔杆子打在了郭景才的腿上,把郭景才的腿砸瘤了,捞着瘤腿跑出车院,其他人看见保长跑了,也都撒腿跑掉了。爷爷孙子三辈子把抓兵的人打着撵掉,解开了老大身上的绳子,穿好衣服,夜晚兄弟们再没有在屋里睡觉,躲在北大滩上的双沙窝。第二天逃往古浪县的大靖,到1949年秋永昌解放后才回到家里。
在当时旧政府把抓兵催粮催草当作头等任务,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抓兵抓壮丁应付征集兵役的任务。赵开福兄弟外逃古浪没有抓住,过了十多天的一个深夜里。保长郭景才又领乡保丁和甲长前去抓赵开敬,一阵紧促的狗吠声把赵开敬惊醒,急穿衣服忙出门,去看狗吠的是什么东西?开门刚迈出门一步,不料抓兵的已人扑到门前。保长郭景才大声下令:“还不动手等啥?”在那紧迫关头下,赵开敬立感大事不妙,急退一步到门里,顺手在门背后摸着了他准备下的铁挑钎子,一个蹦子跳在炕上,双手紧端挑钎子,大声喝道:“来吧!哪个不怕死的,就上前来动手抓来,看谁能把老子抓去?”乡丁祁尚义端着步枪对着赵开敬威胁,但赵开敬拍着胸脯说:“有本事,朝这些开枪。”赵开敬两年前被抓去,张掖驻军服过两年兵役。当过兵的人有胆量,敢于反抗。保长郭景才闯进屋里去抓人,赵开敬猛刺一挑钎子,把郭景才的皮袄捅了一个大口,吓的郭景才急忙跑出门外,再不敢进屋抓人。
那夜晚的赵开敬豁出生命勇敢反抗,乡丁不敢开枪,保甲长、保丁都不敢上前抓人,相持了两个多时辰。他们面对被抓的人,毫无办法,只得灰溜溜的离开。旧社会有句话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谁说当兵的好,爬冰卧雪谁知道。”一说当兵充军比蹲监狱还可怕,老百姓非常厌恶国民政府的强行征兵的劣行。采取各种方法来抵制反抗征兵,出家外逃的,砍掉右手食指的,到远处亲戚家躲避的,晚上不在家里睡觉的。那时代避兵是一大事情,那时的青年人一旦被抓去充军其后果结局不堪设想。四十年代初赵开有六月被抓去充军,在武威东关光明寺驻军,八月双目失明,九月部队开往绥远,失明士兵用绳拴膊牵拉到北套后病故,妻和两岁的幼儿抛在家中。
断指
一个人身上有点残疾乃是终身的痛苦,谁愿意身带残疾?这个小故事的主人把自己身体致成了残疾。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的永宁乡郑家堡有户姓张的人家,兄弟三人,上有父母在世,下有妻子儿女。家境虽然不甚富裕,生活贫淡,但还能兑凑着过得去。由于生活吃紧,战火连绵不断,兵丁徭役,苛捐杂税沉重的压在穷苦老百姓的身上,直不起腰来喘不过气来。这家兄弟三人都是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的青壮年,抓他们其中的那位当壮丁充兵役都是逃不掉的。
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代,兄弟三人采取了分奔东西,各逃兵灾,躲避兵荒。老大逃出家门到外边较远的地方打工避兵;老二领的妻子儿女外流新疆;只有老小,上离不开父母,下丢不下妻子儿女。一家人提心吊胆,惊恐不安。白天老远瞭见有三、五人前来,急忙跑出庄门去到沙堆柴湾藏下,家里的父母妻子瞭哨,等到人走远了再去柴湾喊回来。有时晚上一听狗吠声就跑出去躲避,彻夜不能睡觉,思前想后这样的躲避终究不是个头。“把这个贼娃子社会多时才活出个人来哩?”经过多少个夜晚的思虑,想出了个断指抗兵的办法,他用斧头把自己右手食指剁掉。抓兵的抓去,验兵的一看食指没有了是个废人,当兵的没有食指怎么抠扳机打枪,他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后来的日月里,乡丁保甲长再也不去抓他了。
时光流逝,艰难的熬到了1949年的秋季,1949年秋季的八九月份永昌解放了,此年的秋冬季非常的平静。在外避兵逃难的人陆续全都回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年关春节,全家人欢聚一堂,各抒情怀,都说可恶的兵荒马乱的日月过去了,今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过的。都觉着老小为了这个家,为了父母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断指成了残疾人,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可是老小却认为:“断掉指头,避掉了兵灾,照管了年迈的父母,又保全了一家人的生存,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决不后悔。”能在那个黑暗社会里,安全生存下来的穷苦人,那是相当很少的。(讲述人:王金,男,84岁,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