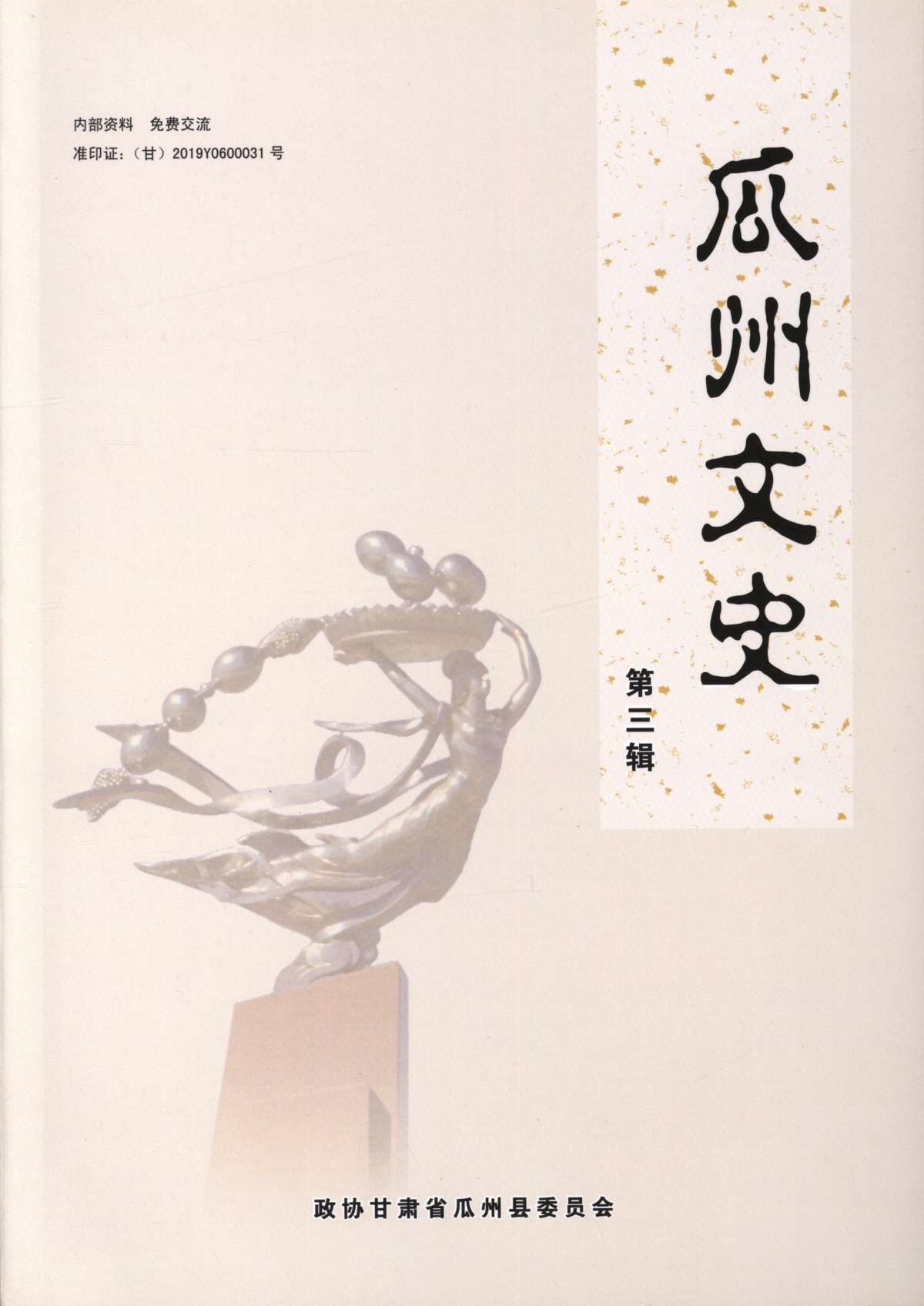内容
我的知青生活片断小忆
刘守成
公元1974年初夏的一天,一批兰州高中毕业生,告别城市、学校、老师,告别了生养他们的父母,坐上了西去的列车,踏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征程,走进社会这个大熔炉,去广阔天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那年不足19岁,正是血气方刚、充满幻想、活蹦乱跳、浑身散发着青春朝气的年纪。离开城市,登上列车,我们全然不顾父母眼中饱含热泪的目光,好似无事一般,同学校领导和家长们挥手相别。
火车汽笛拉响,列车在欢快的乐曲中缓缓起步。“再见!再见!” 声逐渐消失,车箱中一片喧闹。这时,在车箱的一角中不知是谁发出了唏唏的抽泣声,引起几位女生的嘤嘤哭泣,车箱内顿时哭声一片。毕竟还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便阴雨连绵,带队的教师和随送的家长代表不免也神情黯淡,不住地安慰着那些哭泣的学生。不知又是谁高声提议,“让我们唱支歌吧!”立即有人吹响了随身携带的口琴。“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歌声渐渐盖住了哭声,那几个哭得很厉害的女生还没抹去眼角的泪水便也加入了唱歌人的队伍中,歌声像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歌声伴随着车轮锵锵声远去。
列车西行了一天一夜,先是到达塞外边关嘉峪关车站。我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高兴地提起行李蜂拥着下了火车。这时带队老师说:“同学们先下车,但这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转车西行。” 同学们随着老师来到一处公寓,据说等很久才能换乘另一列火车。由于是候车,大家也不敢远离车站,只是在车站附近转悠。有几个胆大的男同学提议到远处去玩玩,但人生地不熟,没能去成。
下午5时许,我们全体又乘上了一列西去的火车。这天,车箱中的喧闹声显然没有第一天那么火爆,大家不时问老师还有多远,老师耐心地说“快啦,快啦”安慰着大家。夜幕降临了,兴奋了一天的同学们渐渐闭上了眼睛,东倒西歪地在座椅上进入了梦乡。不知谁在喃喃细语“再见,妈妈!”噢,他原来是在说梦话。
第二天,天刚亮,醒来的同学们不住地向车窗外张望,眼前没了房屋、村庄,只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茫茫戈壁,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只知是上山下乡去很远的农村。
不九,火车停在了一个叫桥湾的小站上。老师催促着同学们下车,大家还不知所措,没有人抢着下车,这么荒凉的一个小车站,难道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这时,车站下面响起一片锣鼓声、欢迎声,使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原来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在车站进行了短暂的欢迎仪式后,我们一同来的60多位同学被热情的人们抢”上了一辆辆披红挂彩的马车。马车还真多,俨然一个小马车队。
在“叮当”的马铃声和“笃笃”的马蹄声中,马车转过了几道山弯,越过了一条不太深的小河,同学们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被前方一片片绿油油的农田,整齐的林带所吸引。两天来,还没见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ー安西县布隆吉公社。据说,布隆吉这个词蒙语意为“水草茂盛的地方”,难怪这么美丽。
我们被马车拉到了离火车站30多里远的一个叫潘家庄的地方,这天是1974年6月20日。
从地图上看,安西县离兰州一千多公里,在河西走廊最西端,我们所在的布隆吉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公社,除种植小麦、玉米蚕豆等农作物外,此地还有大片的草场,成群的牛羊,更有那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纯朴的农民。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耕种条件,农田、林带、渠道、乡间道路、天然草滩更是一望无边。这里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更没有城市车水马龙般的喧闹,有的是蓝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哞咩”的牛羊欢叫声和鸡犬的鸣叫声。同城市相比,天空在这里蓝了许多,土地广阔了许多,农舍宁静了许多。这就是我对安西县农村的第一印象。
我们7男4女11名知青被分在布隆吉公社潘家庄大队第二生产队。这个队有20来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苦,居住的是土木结构的居民点,ー家挨ー家的小院落,三、四间不高的土坯房。我们当时住在生产队的两间库房内,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住在队长家一间临街的小房子内,一铺土坑,一张旧木桌,两把旧木凳,房内还算干净整洁。房主人热情大方,男主人叫李登富,女主人叫方桂兰,两个男孩,大的不到10岁,小的还在跚跚学步,是一个较和谐的家庭。没过多久,生产队给我们修了一院住房,一排座北朝南五间房子,每间房内两铺小炕,一张没刷油漆的三屉新木桌和两把新木凳。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和全部家当。
当时生产队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城里娃娃们的生活,不但新修了住房,还专门选派了一位大婶为我们做饭,每天记9分工。这位大婶十分勤快辛劳,每天为两顿饭忙得满头大汗。一到开饭时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刻,锅碗瓢盆声,同学们的笑语声融为一体。不论什么饭大家都吃得特别香。每到此时,大婶总是笑眯眯地瞅着我们吃饭,一天的辛劳化作了慈祥的微笑。大婶为我们做饭大概半年多时间,我们不能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最后决定由我们自己学习做饭,每天也记9分工。这下可热闹了,以往在家帮助母亲做过点家务或者有点做饭基础的还好说,有个别同学纯粹没有做过家务事,学习做饭便成了我们面向生活的第一件事。学和面,学烧火,一切从头学起。好在当时饭食十分简单,不是一大锅汤面条,就是每人一大碗干面条,或是两个大馒头,蔬菜很少,但能保证大家吃饱肚子,这种生活在七十年代就很不错了。听在兰州以东或以南插队的同学说吃不饱肚子是常事。甘肃农村本来就很贫穷,当时还有不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一想起这,我们反而觉得十分庆幸和骄傲,因为我们当时基本没有饿肚子。
才到农村,不会劳动,社员见我们干活的样子常常发笑,但还是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们。记得第一次干活,队长十分照顾我们,派我们随几位妇女去村边不远的羊圈起粪推粪。原以为干这种活很脏,都不愿去。但到现场一看,并非想象中的那种粪,而是在羊圈里一层层加土,直到一定厚度后便用镢头将羊群踏实的“粪”刨开,再装在架子车里推到圈外酥散的“粪”堆上,这便是上好的农家肥。农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那很少使用化肥的年代,这种土粪肥确实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肥料,它为保证农作物丰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甩开膀子干起来。才开始干农活,不会合理分配气力,猛干一阵子,后劲跟不上,那几位妇女反复说“慢慢干,慢慢干”,看着我们单薄的身体和不惜力气的样子都很心痛,不时给我们递水,让我们擦汗,我们也顾不了这些,反倒越干越欢。我们男学生干热了总爱脱掉外衣,穿件小背心赤着胳膊,这时总有热心的大娘大婶或老农关心地劝我们说:“娃娃,穿上上衣,要不会晒脱皮的”。我们反倒纳闷,那么热的天气,年轻妇女总是头裹围巾,脸戴口罩,包了个严严实实,反说这样不热。后来才明白,这种方式不乏为河西农村妇女的一种防晒、防寒、防风吹的好方法。
劳动一天下来,个个都累得腰酸腿疼,但很少有人叫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得从这一天开始。好在我们都很年轻,晚上一觉醒来,头天的疲劳顿觉消失,新的一天又精神饱满。这样我们初步闯过了劳动的第一关。
夏收开始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收割小麦。天不亮,队长就挨门喊我们起床。由于劳累,个个都想多睡一会,清晨的瞌睡最宝贵,都不想起床,这样就遭来队长的大声呵斥,我们不情愿地起床随队长上地。到了地头,队长便一个个地把我们分散指派到社员中间,跟着学习割麦。头几天,我们割得很少,而且不是割破手指便是割破自己脚上的胶鞋,很是狼狈。社员们也不愿意带我们割麦,这样反倒耽误他们的事。由于当时没有承包制,一块地只要大伙儿割完都能记上工分,因此也不太计较我们。我们小伙子还有点力气,便让我们学捆麦子。没几天,满手被“葽子”勒岀了血泡,胳膊肘和膝盖磨得通红,非常结实的劳动布工作服(父母们发的)不几日便在胳膊肘处和膝盖处磨破了,不得不打上厚厚的补丁。
就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我们不仅学会了割麦子、捆麦子,还会了转捆子、码垛子、套车吆喝牲口等农活,甚至有的还学会了打场、扬场这种老农才会干的细活。农民们赞许说:“这些娃娃是好样的!”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不容易,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更坚定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信心。
一到冬天,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天寒地冻、寒风凛冽,谁都不愿出门。冬季农活少,一天日子短,在屋子里的时间多。在外干活较集中,就是推粪、翻粪,为来年准备农家肥。再就是集中平田整地,到滩上去拾牛粪等。上滩拾粪要起得很早,天不亮就出门,一挂马车或牛车,三、四个人,拾得快些下午早早就回来了,拾得慢些赶太阳落山也能拾满一大车,大概那么一、两方粪,大家也记同样的工分。一个冬季仅仅拾粪还不行,经大队研究成立了一个以知青为主(这时三个队都有知青),由大队民兵连长刘治富负责的平田整地专业队。所谓专业队,也就是知青多点,农活单一点,不再分散。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排练文艺节目,这样正好发挥了这些城市学生的特长。这批知青中,吹拉弹唱跳,编导演各路人才都有。一说演节目,可乐坏了他们,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排练出一台像模像样的文艺节目来,不但在本大队演出,还参加了公社的汇演和县上的文艺汇演,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由于我们的节目出色,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人都没有回兰州过年,而是同贫下中农共度春节,我们的节目还被离我们30里开外的双塔大队请去演了几场。一个春节下来,我们同农民的感情更加贴近了,农民也更喜爱我们这些城市娃娃。
初春,是当时农村最忙的一个季节。“一年之际在于春”,说明春季对农村的重要性。我记起拉工备耕这个农活,天还很黑,三星还在头顶上,我便同一个“车夫”去套皮车拉粪上地。拉一趟粪从装车到卸车,根据地段远近一趟下来远的40来分钟,近的十几分钟,往往装满一车,一坐到车上就睡着了,那些草木粪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装上车热气腾腾,睡在上面很“舒服”。久而久之,我从那时起便落下个腰疼病,老农说是在潮粪堆上“潮” 出的病。当然,我并没有在意,这点困难算什么!春播一开始,大地复苏,春暖柳叶开,到处一派春机盎然。人和动植物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磨熬,这下都舒展了筋骨,活蹦乱跳。按老农的话说“蹦子跳得格外高”。春播的农活很多,要求的技艺也很高,套车耕地,拉耙搂地,掌搂点播,这些不是我们随便就能学会的。深感遗憾的是,那些活我除了能套头老牛歪歪扭扭犁几条沟外,很多农活都没有学会。一个春天下来,土地播下了种子,更播下了农民们的希望,也播下了我们这些知青的美好愿望。
四有几件事使我特别难忘。
一件是74年7月份的一天。天刚黑下来没多久,大约10点多钟,我们知青点的人吃过晚饭,大家有说有笑,有的在下棋聊天,瓜蝌夂史第3辑有的在清洗一天的疲劳,有的则在灯下写着什么,这是个难得的休闲时刻。这时,突听门外脚步急促,一个人连喊带跑向队长家急速奔去,只听“队长!不好啦,南边的水坝跑水啦”。这个消息不一会便传遍全队家家户户。报警声就是命令,容不得我们犹豫,大家不约而同随着人流向大坝跑去。队长边跑边喊“背上麦草, 拿上椽子”。我们也来不及拿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劲地跑,天黑路又不好,高一脚低一脚奋力向大坝跑去。大坝离居民点大概三、四里地,我们先到的几个知青气喘嘘嘘,跑到坝上一看,由于下雨发洪水,把大坝拉开了一个2米多的口子,大水咆哮着卷着浊泥带着柴草向低处冲去。怎么办,眼看着集体财产就要毁于一旦,我们几个会水的知青先后“扑通”地跳进水中,用身体去堵缺口。这时后面赶上来的人群有的向我们扔出了大绳,有的递过来椽子麦草什么的,队长指挥着在缺口处打木桩,压椽子,塞麦草。人多力量大,大约半个来小时的功夫便堵住了水口子,我们被从水中拉上来时已筋疲力尽,一个个倒在了坝上。我们的身上、腿上、脚上到处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我脚上的鞋也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看到集体财产安然无恙,大家总算松了口气。我们的行动,给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自己也经受了一次较大的考验。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5年5月的一天。副队长李珍领着4个女社员5个男女知青,乘坐两辆皮车去河坝湾上拔蒿子。蒿子是很好的草木肥,壅在地里作物生长得特别茂盛。到了河坝,我们认真地拔起了蒿子,手上磨起了血泡也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的拔。几个时辰下来,便拔了满满两大车蒿子,大家兴高采烈地坐在高高的蒿子车上,唱着歌儿踏上了归途。皮车正顺着河坝弯弯曲曲的小路行进时,一辆皮车陷进了河坝的软泥中,大家急忙跳下车帮助推车,但是车越陷越深,半个车轮陷进了泥沙中,连掌辕的辕马也陷进不能自拔。我们使劲喊着号子,肩扛头顶手推都无济于事,三匹马也失去它们应有的战斗力,只是喘着粗气昂着头嗷嗷直叫。就在人困马乏之际,只见车夫手拿镰刀猛敲车辕上的铁环,不知是人来了精神还是马受了惊吓,辕马长啸一声,忽”的从泥浆中站立起来,把陷在泥中的车拖了岀来。也就在这一霎那间,由于辕马猛然发力,致使马车尾部猛向左一摆,把后面推车的两个人甩了个趔趄,而我正手抱肩扛车辕条,车尾部向左摆时,车辕向右猛摆,我顿时两脚离地身体悬空被挂在车辕上。不知谁喊了一声“危险”!车辕又猛然向左摆回来,我便象一只猴子似的被远远抛在5米开外。马车终于拉了出来,我却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很久没能爬起来。这时大家围过来,问这问那,我从地上爬起来,还好,没有伤着什么地方,仅仅是让大家惊吓了一场。有人对正在发愣的副队长说:“好险呀,如果把知青给压了,就有你的好看啦!”副队长确实吓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我从大家的语言中感悟到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是何等的爱护。
当然,知青生活远不止这些。我们有过许多欢乐和喜悦,但也有过彷徨和沮丧,更有几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一个时期个别好动的知青总是喜欢走村串点互相串联玩耍,这就难免引一些事端来,如打个架,闹个恶作剧什么的。较有影响的当数1975年“3.8”事件。(“事件”是笔者个人看法)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公社为召开“三干会”放了一场电影。当时能看场电影就是最大的文化享受了,那场面人多得比什么都热闹。这期间潘家庄一队有个叫杨金山的知青和布隆吉的两名知青不知什么原因打起架来,顿时秩序大乱,一时由三人打架发展到十几人打群架。为了制止这个小“骚乱”,当时一位在场的领导说了句“你们的民兵是干什么的?请把秩序维持一下!”只听几声哨响,出来一队民兵,把闹得最凶的两位布隆吉知青给“请”了出去,并且关在了房子里。两位知青并不示弱,没多久便从门上的小窗中爬出跑掉。第二天春耕动员大会正在召开,领导的动员报告没作多久,这时场外一阵骚动,来了十几名手持棍棒、砖块的知青,大喊“昨晚谁捆了我们知青,站出来! ”话音未落只见一阵小砖头碎石块向会场人群中袭来,会场象开了锅的粥沸腾起来。由于事发突然,来势凶猛,人们还不知所措,也没有人上前制止,大会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来解决问题。知青的理由是昨晚民兵捆打了他们,他们要找那些人算账,当时的公社领导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没有与这些知青计较,而是好言相劝,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并作岀让步,安排他们吃饭,然后用一辆解放牌卡车把这些知青一一送回去。一段时间,这些参与闹事的知青很不冷静,时不时聚众打架闹事,使许多社员群众闻知青色变,避而远之。这件事,由于没有认真追究责任,个别知青难以把握自己,事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而疏远了知青同社员群众的关系,一时助长了一些知青的不良习气。
五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它既造就了一批先进青年,同时也给历史留下了一道痕迹。为了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满怀一腔热血,离开城市,离开父母,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在农村边疆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开辟了城市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课堂。他们有的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更多的却象夜空一闪即逝的流星,没有留下更多的闪光点。
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在人生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它却是极其珍贵的。这段生活结束后,我的人生又经历了招工、参军、入党、提干,由一个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国家干部,并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在安西一“蹴”就是二十五个春秋。安西接受了我,我也爱上了安西,就像一棵树苗,在安西扎了根,为建设安西做岀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回眸人生,我是无悔的。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走向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留恋这段生活,更感谢安西的土地培育了我。我且以两年多的平凡经历来诉说一段不完整的故事,以引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刘守成
公元1974年初夏的一天,一批兰州高中毕业生,告别城市、学校、老师,告别了生养他们的父母,坐上了西去的列车,踏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征程,走进社会这个大熔炉,去广阔天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那年不足19岁,正是血气方刚、充满幻想、活蹦乱跳、浑身散发着青春朝气的年纪。离开城市,登上列车,我们全然不顾父母眼中饱含热泪的目光,好似无事一般,同学校领导和家长们挥手相别。
火车汽笛拉响,列车在欢快的乐曲中缓缓起步。“再见!再见!” 声逐渐消失,车箱中一片喧闹。这时,在车箱的一角中不知是谁发出了唏唏的抽泣声,引起几位女生的嘤嘤哭泣,车箱内顿时哭声一片。毕竟还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便阴雨连绵,带队的教师和随送的家长代表不免也神情黯淡,不住地安慰着那些哭泣的学生。不知又是谁高声提议,“让我们唱支歌吧!”立即有人吹响了随身携带的口琴。“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歌声渐渐盖住了哭声,那几个哭得很厉害的女生还没抹去眼角的泪水便也加入了唱歌人的队伍中,歌声像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歌声伴随着车轮锵锵声远去。
列车西行了一天一夜,先是到达塞外边关嘉峪关车站。我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高兴地提起行李蜂拥着下了火车。这时带队老师说:“同学们先下车,但这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转车西行。” 同学们随着老师来到一处公寓,据说等很久才能换乘另一列火车。由于是候车,大家也不敢远离车站,只是在车站附近转悠。有几个胆大的男同学提议到远处去玩玩,但人生地不熟,没能去成。
下午5时许,我们全体又乘上了一列西去的火车。这天,车箱中的喧闹声显然没有第一天那么火爆,大家不时问老师还有多远,老师耐心地说“快啦,快啦”安慰着大家。夜幕降临了,兴奋了一天的同学们渐渐闭上了眼睛,东倒西歪地在座椅上进入了梦乡。不知谁在喃喃细语“再见,妈妈!”噢,他原来是在说梦话。
第二天,天刚亮,醒来的同学们不住地向车窗外张望,眼前没了房屋、村庄,只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茫茫戈壁,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只知是上山下乡去很远的农村。
不九,火车停在了一个叫桥湾的小站上。老师催促着同学们下车,大家还不知所措,没有人抢着下车,这么荒凉的一个小车站,难道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这时,车站下面响起一片锣鼓声、欢迎声,使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原来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在车站进行了短暂的欢迎仪式后,我们一同来的60多位同学被热情的人们抢”上了一辆辆披红挂彩的马车。马车还真多,俨然一个小马车队。
在“叮当”的马铃声和“笃笃”的马蹄声中,马车转过了几道山弯,越过了一条不太深的小河,同学们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被前方一片片绿油油的农田,整齐的林带所吸引。两天来,还没见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ー安西县布隆吉公社。据说,布隆吉这个词蒙语意为“水草茂盛的地方”,难怪这么美丽。
我们被马车拉到了离火车站30多里远的一个叫潘家庄的地方,这天是1974年6月20日。
从地图上看,安西县离兰州一千多公里,在河西走廊最西端,我们所在的布隆吉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公社,除种植小麦、玉米蚕豆等农作物外,此地还有大片的草场,成群的牛羊,更有那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纯朴的农民。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耕种条件,农田、林带、渠道、乡间道路、天然草滩更是一望无边。这里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更没有城市车水马龙般的喧闹,有的是蓝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哞咩”的牛羊欢叫声和鸡犬的鸣叫声。同城市相比,天空在这里蓝了许多,土地广阔了许多,农舍宁静了许多。这就是我对安西县农村的第一印象。
我们7男4女11名知青被分在布隆吉公社潘家庄大队第二生产队。这个队有20来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苦,居住的是土木结构的居民点,ー家挨ー家的小院落,三、四间不高的土坯房。我们当时住在生产队的两间库房内,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住在队长家一间临街的小房子内,一铺土坑,一张旧木桌,两把旧木凳,房内还算干净整洁。房主人热情大方,男主人叫李登富,女主人叫方桂兰,两个男孩,大的不到10岁,小的还在跚跚学步,是一个较和谐的家庭。没过多久,生产队给我们修了一院住房,一排座北朝南五间房子,每间房内两铺小炕,一张没刷油漆的三屉新木桌和两把新木凳。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和全部家当。
当时生产队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城里娃娃们的生活,不但新修了住房,还专门选派了一位大婶为我们做饭,每天记9分工。这位大婶十分勤快辛劳,每天为两顿饭忙得满头大汗。一到开饭时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刻,锅碗瓢盆声,同学们的笑语声融为一体。不论什么饭大家都吃得特别香。每到此时,大婶总是笑眯眯地瞅着我们吃饭,一天的辛劳化作了慈祥的微笑。大婶为我们做饭大概半年多时间,我们不能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最后决定由我们自己学习做饭,每天也记9分工。这下可热闹了,以往在家帮助母亲做过点家务或者有点做饭基础的还好说,有个别同学纯粹没有做过家务事,学习做饭便成了我们面向生活的第一件事。学和面,学烧火,一切从头学起。好在当时饭食十分简单,不是一大锅汤面条,就是每人一大碗干面条,或是两个大馒头,蔬菜很少,但能保证大家吃饱肚子,这种生活在七十年代就很不错了。听在兰州以东或以南插队的同学说吃不饱肚子是常事。甘肃农村本来就很贫穷,当时还有不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一想起这,我们反而觉得十分庆幸和骄傲,因为我们当时基本没有饿肚子。
才到农村,不会劳动,社员见我们干活的样子常常发笑,但还是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们。记得第一次干活,队长十分照顾我们,派我们随几位妇女去村边不远的羊圈起粪推粪。原以为干这种活很脏,都不愿去。但到现场一看,并非想象中的那种粪,而是在羊圈里一层层加土,直到一定厚度后便用镢头将羊群踏实的“粪”刨开,再装在架子车里推到圈外酥散的“粪”堆上,这便是上好的农家肥。农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那很少使用化肥的年代,这种土粪肥确实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肥料,它为保证农作物丰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甩开膀子干起来。才开始干农活,不会合理分配气力,猛干一阵子,后劲跟不上,那几位妇女反复说“慢慢干,慢慢干”,看着我们单薄的身体和不惜力气的样子都很心痛,不时给我们递水,让我们擦汗,我们也顾不了这些,反倒越干越欢。我们男学生干热了总爱脱掉外衣,穿件小背心赤着胳膊,这时总有热心的大娘大婶或老农关心地劝我们说:“娃娃,穿上上衣,要不会晒脱皮的”。我们反倒纳闷,那么热的天气,年轻妇女总是头裹围巾,脸戴口罩,包了个严严实实,反说这样不热。后来才明白,这种方式不乏为河西农村妇女的一种防晒、防寒、防风吹的好方法。
劳动一天下来,个个都累得腰酸腿疼,但很少有人叫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得从这一天开始。好在我们都很年轻,晚上一觉醒来,头天的疲劳顿觉消失,新的一天又精神饱满。这样我们初步闯过了劳动的第一关。
夏收开始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收割小麦。天不亮,队长就挨门喊我们起床。由于劳累,个个都想多睡一会,清晨的瞌睡最宝贵,都不想起床,这样就遭来队长的大声呵斥,我们不情愿地起床随队长上地。到了地头,队长便一个个地把我们分散指派到社员中间,跟着学习割麦。头几天,我们割得很少,而且不是割破手指便是割破自己脚上的胶鞋,很是狼狈。社员们也不愿意带我们割麦,这样反倒耽误他们的事。由于当时没有承包制,一块地只要大伙儿割完都能记上工分,因此也不太计较我们。我们小伙子还有点力气,便让我们学捆麦子。没几天,满手被“葽子”勒岀了血泡,胳膊肘和膝盖磨得通红,非常结实的劳动布工作服(父母们发的)不几日便在胳膊肘处和膝盖处磨破了,不得不打上厚厚的补丁。
就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我们不仅学会了割麦子、捆麦子,还会了转捆子、码垛子、套车吆喝牲口等农活,甚至有的还学会了打场、扬场这种老农才会干的细活。农民们赞许说:“这些娃娃是好样的!”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不容易,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更坚定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信心。
一到冬天,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天寒地冻、寒风凛冽,谁都不愿出门。冬季农活少,一天日子短,在屋子里的时间多。在外干活较集中,就是推粪、翻粪,为来年准备农家肥。再就是集中平田整地,到滩上去拾牛粪等。上滩拾粪要起得很早,天不亮就出门,一挂马车或牛车,三、四个人,拾得快些下午早早就回来了,拾得慢些赶太阳落山也能拾满一大车,大概那么一、两方粪,大家也记同样的工分。一个冬季仅仅拾粪还不行,经大队研究成立了一个以知青为主(这时三个队都有知青),由大队民兵连长刘治富负责的平田整地专业队。所谓专业队,也就是知青多点,农活单一点,不再分散。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排练文艺节目,这样正好发挥了这些城市学生的特长。这批知青中,吹拉弹唱跳,编导演各路人才都有。一说演节目,可乐坏了他们,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排练出一台像模像样的文艺节目来,不但在本大队演出,还参加了公社的汇演和县上的文艺汇演,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由于我们的节目出色,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人都没有回兰州过年,而是同贫下中农共度春节,我们的节目还被离我们30里开外的双塔大队请去演了几场。一个春节下来,我们同农民的感情更加贴近了,农民也更喜爱我们这些城市娃娃。
初春,是当时农村最忙的一个季节。“一年之际在于春”,说明春季对农村的重要性。我记起拉工备耕这个农活,天还很黑,三星还在头顶上,我便同一个“车夫”去套皮车拉粪上地。拉一趟粪从装车到卸车,根据地段远近一趟下来远的40来分钟,近的十几分钟,往往装满一车,一坐到车上就睡着了,那些草木粪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装上车热气腾腾,睡在上面很“舒服”。久而久之,我从那时起便落下个腰疼病,老农说是在潮粪堆上“潮” 出的病。当然,我并没有在意,这点困难算什么!春播一开始,大地复苏,春暖柳叶开,到处一派春机盎然。人和动植物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磨熬,这下都舒展了筋骨,活蹦乱跳。按老农的话说“蹦子跳得格外高”。春播的农活很多,要求的技艺也很高,套车耕地,拉耙搂地,掌搂点播,这些不是我们随便就能学会的。深感遗憾的是,那些活我除了能套头老牛歪歪扭扭犁几条沟外,很多农活都没有学会。一个春天下来,土地播下了种子,更播下了农民们的希望,也播下了我们这些知青的美好愿望。
四有几件事使我特别难忘。
一件是74年7月份的一天。天刚黑下来没多久,大约10点多钟,我们知青点的人吃过晚饭,大家有说有笑,有的在下棋聊天,瓜蝌夂史第3辑有的在清洗一天的疲劳,有的则在灯下写着什么,这是个难得的休闲时刻。这时,突听门外脚步急促,一个人连喊带跑向队长家急速奔去,只听“队长!不好啦,南边的水坝跑水啦”。这个消息不一会便传遍全队家家户户。报警声就是命令,容不得我们犹豫,大家不约而同随着人流向大坝跑去。队长边跑边喊“背上麦草, 拿上椽子”。我们也来不及拿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劲地跑,天黑路又不好,高一脚低一脚奋力向大坝跑去。大坝离居民点大概三、四里地,我们先到的几个知青气喘嘘嘘,跑到坝上一看,由于下雨发洪水,把大坝拉开了一个2米多的口子,大水咆哮着卷着浊泥带着柴草向低处冲去。怎么办,眼看着集体财产就要毁于一旦,我们几个会水的知青先后“扑通”地跳进水中,用身体去堵缺口。这时后面赶上来的人群有的向我们扔出了大绳,有的递过来椽子麦草什么的,队长指挥着在缺口处打木桩,压椽子,塞麦草。人多力量大,大约半个来小时的功夫便堵住了水口子,我们被从水中拉上来时已筋疲力尽,一个个倒在了坝上。我们的身上、腿上、脚上到处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我脚上的鞋也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看到集体财产安然无恙,大家总算松了口气。我们的行动,给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自己也经受了一次较大的考验。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5年5月的一天。副队长李珍领着4个女社员5个男女知青,乘坐两辆皮车去河坝湾上拔蒿子。蒿子是很好的草木肥,壅在地里作物生长得特别茂盛。到了河坝,我们认真地拔起了蒿子,手上磨起了血泡也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的拔。几个时辰下来,便拔了满满两大车蒿子,大家兴高采烈地坐在高高的蒿子车上,唱着歌儿踏上了归途。皮车正顺着河坝弯弯曲曲的小路行进时,一辆皮车陷进了河坝的软泥中,大家急忙跳下车帮助推车,但是车越陷越深,半个车轮陷进了泥沙中,连掌辕的辕马也陷进不能自拔。我们使劲喊着号子,肩扛头顶手推都无济于事,三匹马也失去它们应有的战斗力,只是喘着粗气昂着头嗷嗷直叫。就在人困马乏之际,只见车夫手拿镰刀猛敲车辕上的铁环,不知是人来了精神还是马受了惊吓,辕马长啸一声,忽”的从泥浆中站立起来,把陷在泥中的车拖了岀来。也就在这一霎那间,由于辕马猛然发力,致使马车尾部猛向左一摆,把后面推车的两个人甩了个趔趄,而我正手抱肩扛车辕条,车尾部向左摆时,车辕向右猛摆,我顿时两脚离地身体悬空被挂在车辕上。不知谁喊了一声“危险”!车辕又猛然向左摆回来,我便象一只猴子似的被远远抛在5米开外。马车终于拉了出来,我却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很久没能爬起来。这时大家围过来,问这问那,我从地上爬起来,还好,没有伤着什么地方,仅仅是让大家惊吓了一场。有人对正在发愣的副队长说:“好险呀,如果把知青给压了,就有你的好看啦!”副队长确实吓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我从大家的语言中感悟到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是何等的爱护。
当然,知青生活远不止这些。我们有过许多欢乐和喜悦,但也有过彷徨和沮丧,更有几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一个时期个别好动的知青总是喜欢走村串点互相串联玩耍,这就难免引一些事端来,如打个架,闹个恶作剧什么的。较有影响的当数1975年“3.8”事件。(“事件”是笔者个人看法)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公社为召开“三干会”放了一场电影。当时能看场电影就是最大的文化享受了,那场面人多得比什么都热闹。这期间潘家庄一队有个叫杨金山的知青和布隆吉的两名知青不知什么原因打起架来,顿时秩序大乱,一时由三人打架发展到十几人打群架。为了制止这个小“骚乱”,当时一位在场的领导说了句“你们的民兵是干什么的?请把秩序维持一下!”只听几声哨响,出来一队民兵,把闹得最凶的两位布隆吉知青给“请”了出去,并且关在了房子里。两位知青并不示弱,没多久便从门上的小窗中爬出跑掉。第二天春耕动员大会正在召开,领导的动员报告没作多久,这时场外一阵骚动,来了十几名手持棍棒、砖块的知青,大喊“昨晚谁捆了我们知青,站出来! ”话音未落只见一阵小砖头碎石块向会场人群中袭来,会场象开了锅的粥沸腾起来。由于事发突然,来势凶猛,人们还不知所措,也没有人上前制止,大会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来解决问题。知青的理由是昨晚民兵捆打了他们,他们要找那些人算账,当时的公社领导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没有与这些知青计较,而是好言相劝,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并作岀让步,安排他们吃饭,然后用一辆解放牌卡车把这些知青一一送回去。一段时间,这些参与闹事的知青很不冷静,时不时聚众打架闹事,使许多社员群众闻知青色变,避而远之。这件事,由于没有认真追究责任,个别知青难以把握自己,事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而疏远了知青同社员群众的关系,一时助长了一些知青的不良习气。
五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它既造就了一批先进青年,同时也给历史留下了一道痕迹。为了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满怀一腔热血,离开城市,离开父母,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在农村边疆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开辟了城市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课堂。他们有的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更多的却象夜空一闪即逝的流星,没有留下更多的闪光点。
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在人生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它却是极其珍贵的。这段生活结束后,我的人生又经历了招工、参军、入党、提干,由一个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国家干部,并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在安西一“蹴”就是二十五个春秋。安西接受了我,我也爱上了安西,就像一棵树苗,在安西扎了根,为建设安西做岀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回眸人生,我是无悔的。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走向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留恋这段生活,更感谢安西的土地培育了我。我且以两年多的平凡经历来诉说一段不完整的故事,以引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相关人物
刘守成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