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信使:宋初沙州和甘州的通使与联系
| 内容出处: | 《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1820020220000454 |
| 颗粒名称: | 丝绸之路上的信使:宋初沙州和甘州的通使与联系 |
| 分类号: | K928.6 |
| 页数: | 13 |
| 页码: | 74-8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丝绸之路上的信使:宋初沙州和甘州的通使与联系的具体内容,他们围绕着生存与发展,与周边的民族政权或和或战,发展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和联系,是唐末五代宋初藩镇割据政局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集中反映。 |
|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甘州 信使 |
内容
公元9世纪中期(840年左右),唐王朝北疆的回鹘汗国崩溃了,其中的一支回鹘部族迁入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地区。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融合和壮大,这支回鹘部族趁着唐末中原的分裂、藩镇军阀混战的绝好机会,在9世纪末期(890年左右),终于在肥沃的黑河流域甘州(今甘肃张掖)建立起民族政权——史称“甘州回鹘”,并不断地向河西走廊以西发展壮大。从晚唐五代直到宋初,甘州回鹘政权控制着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交通、贸易要道,并在五代中原王朝政权的对峙更替中,成为五代宋初河西地区地缘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围绕着生存与发展,与周边的民族政权或和或战,发展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和联系,是唐末五代宋初藩镇割据政局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集中反映。
关于甘州回鹘的建立始末及甘州回鹘可汗的世次,历来中外学者们研究较多①,经过学者们对传世文献的钩稽考证,其民族政权的建立过程和可汗的世次,基本上清晰地显现出来,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和方便。甘州回鹘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一直也是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关于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关系的研究上,多是对敦煌出土文献里的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于阗文文献进行综合对照,研究的方法和角度越来越呈现出文本细读、材料验证的特征。尽管如此,可其中的一些史事并不鲜明,细节也未完全呈现出来,主要还是文献不足的缘故。笔者以往来于甘州回鹘和敦煌归义军二大政权之间的信使为切入点,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的书信文献的文本细读,管窥宋初沙州和甘州二地之间的通使和联系,以深入探究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关系,从而呈现出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政治生态。
一
从公元9世纪末期甘州回鹘建立胡汉联合政权(即少数回鹘贵族统治绝大多数胡汉民众的联合政权)之日起,甘州回鹘政权就将自己的政权定位为同中原藩镇同等,甚至与周边藩镇割据力量互不统属、军事独立、地位平等的地方藩镇政权,并沿着河西走廊不断向西发展,试图控制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县)、沙州(今甘肃敦煌),进而将整个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控制起来。甘州回鹘在政治上通过朝贡中原王朝,获得中原王朝册封,以承认其政治权力;经济上挟地理之利,与中原王朝、周边藩镇进行货物贸易,影响遍及瓜、沙、于阗等地;军事上凭借优越的骑兵横行河西走廊,对归义军及其他藩镇虎视眈眈,最具军事威胁。
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之间主要是朝贡关系,还有短时期内向唐王朝请求下嫁公主的联姻关系,“除了是继承唐代回鹘与唐王朝甥舅关系的余绪之外,更主要的是使甘州回鹘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支持”①,但中央王朝却将甘州回鹘视为蕃夷和外属。就河西走廊内的藩镇割据势力而言,如河西走廊东段的灵州、凉州等藩镇,西边的归义军藩镇,都将甘州回鹘视为一“道”猃狁。唐末存续下来的藩镇格局关系,尤其是经过中原王朝对甘州回鹘的册封确认之后便固定下来。为甘州回鹘政权与周边藩镇的政治关系奠定了基调,即灵州、凉州、甘州、沙州之间,都是政治地位平等的藩镇关系,而不是政治依附的关系。既然是政治地位平等的藩镇,就存在争夺整个河西走廊控制权的矛盾,因此,在唐末到五代的七十余年间,甘州回鹘凭借切断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道路的优势,积极向西发展势力,吞并了原由敦煌归义军政权控制的肃州,并一度使归义军政权臣服,签订城下之盟。归义军政权一方面不得不主动向甘州回鹘请求下嫁公主以联姻,试图再次打通与中原王朝之间朝贡的交通道路和政治联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政权的安全,也主动与西域的于闻政权进行三次政治联姻,以抗衡甘州回鹘。②联姻与斗争,吞并与反吞并,就成为敦煌与甘州二地政权之间政治关系的一个基调,而最能反映二地之间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的,就是敦煌出土文献里奔走于两地的信使,以及这些信使们传递的信件里透露出来的细节信息。
公元960年,中原宋朝建立之后,敦煌归义军依托与于阗政权之间的亲密联姻关系积极地向刚刚建立的北宋朝廷朝贡,希望重新建立丝绸之路上的传统政治依附关系。962年正月,敦煌归义军将领曹元忠被宋朝廷正式授予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中书令的官衔,归义军得到中原王朝的直接政治支持,使自五代后周以来一度十分紧张的甘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归义军之间的政治关系趋于和缓,而且成为兄弟关系,往来通使不断。笔者通过深入挖掘文献细节,认为促成甘沙关系缓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962年,曹元忠在得到宋朝的官告之后娶于阗王李圣天和非曹夫人所生之女(于阗公主)为妻,敦煌与于阗二地之间形成了第二次政治联姻关系。①这样,曹元忠与于阗王李圣天之间结成了既是郎舅、又是子婿一岳父的双重姻亲关系。这种双重姻亲关系,正是归义军政权联合于阗对抗甘州回鹘政权,重新打开通向中原朝廷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安全保障。962—964年,是沙州、甘州和于阗三地之间的“蜜月期”,双方通使不断,但随着964年九月之后于阗公主和于阗王一起返回于阗,966年于阗王李圣天去世,于阗和敦煌二地之间的政治联姻出现了中断,甘州与沙州的政治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965—967年是河西走廊的多事之秋,西州回鹘政权崩溃,河西民族矛盾交织,甘州和敦煌之间数次通使往来,这些信使传递双方的政治意图,以解决政治纠纷。最有名的一封书信写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是归义军曹元忠派使头阎物成出使甘州,其携带的亲笔信件。从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②,可知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因为甘州回鹘偷劫归义军使人而责难问讯,双方书札往复频繁的情形。
1.信件的书写年代、性质、主要内容和信使
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③
早者,因为有少贼行,已专咨启。近蒙华翰,兼惠厚仪,无任感钦之至。所云:“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闻此嘉言,倍深感仰。况厶忝为眷爱,实惬衷诚。永敦久远之情,固保始终之契。
又云:“在此三五人,往贵道偷来之事况,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厶并不知闻。近者示及,方知子(仔)细。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诸)处官人,必当刑宪!’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人总并散,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劫去)玉□□□,至凉州寻问即是!”(后缺)
上述书信写于丁卯年正月,那么丁卯年是哪一年呢?根据敦煌文献的出土年代,可能是公元907年(唐天祐四年)、967年(宋乾德五年)、1027年(宋天圣五年)中的某一个,根据文献上的其他情况(详见下文)来判断,显然967年最为合适。从书信草稿内容来判断,应当是敦煌地方官给甘州地方官的书信草稿,所以带有草稿涂抹的特征。
由于《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是一封书信的草稿,因此有许多让人困惑而容易理解歧误的地方。比如,发信人和收信人分别是谁呢?对此,有极少意见将其理解为甘州使头代表归义军节度使给甘州回鹘的书信,如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①一文中提到,归义军通
使甘州回鹘时,归义军“专门设立甘州使头以分管甘州使团事宜”,认为甘州使头处理邦交事务,责关重大,因此享有很大的权力,故将P.3272v文书视为甘州使头致回鹘可汗的书状,是甘州使头代表归义军节度使在与甘州可汗进行邦交谈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中认为“此件,由内容看,系致甘州回鹘书”②,但未指出发件人为谁。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这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草稿③。陆庆夫进一步更将P.2155v文书与P.3272v文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关联密切,都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曹元忠姐夫)的书状④。敦煌文献及传世文献显示,967年(宋乾德五年)任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人正是曹元忠。那么,这封书信非常可能就是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名义草拟的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草稿,故称“书本”,本即草稿之意。草稿拟好之后,拟由归义军派出的使头阎物成传递至甘州。书信草稿的正面是丙寅年正月、二月的牧羊人兀宁牒状二件,上有大字的判凭“为凭”及鸟形押,书写的文字特征及鸟形押的类型与曹元忠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的类型十分相近。因此,背面丁卯年的书信草稿应该与正面丙寅年的文书年代十分相近,由于丙寅年之后便是丁卯年,所以,这显然是利用丙寅年存档(为凭证)旧文书的背面起草了书信草稿,丙寅年是公元966年,中原年号是北宋乾德四年。
搞清楚了P.3272v文书的年代、性质和收发对象之后,文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由于书信格式较为特殊,学者们对内容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种意见认为,文中既有甘州回鹘可汗回敦煌曹元忠上一封书信的答书,即书信草稿文中第一段第二行“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的内容,反映甘州与属下各部设盟立誓,不许侵扰归义军境界⑤;也有曹元忠回答甘州回鹘可汗来信中的内容,即书信草稿第二段第四行“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处官人,必当刑宪”⑥,故将文中“又云”部分的内容全部视为曹元忠致书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李正宇先生也持此种观点。在《敦煌学导论》一书附录的《敦煌文献选讲》中,李正宇将P.3272v文书解读为“北宋乾德五年(967)沙州归义军遣使送交甘州回鹘的公文。(公文)内容反映了各自境内不法之徒前往对方境内劫掠以及两邦首脑互相谅解,各自约束本邦以保持友好关系的史实”①,但细读书信内容,如果将第二段“又云”之后的内容理解为曹元忠书信里的内容,显然与文意不合。但如果不这样理解,又与后文的“甘州”二字相矛盾,所以李正宇不得不将后文中的“小镇”解释为“归义军境内负责军事戍守及社会治安的军镇”,是归义军节度使“告知(甘州)近来西州离乱,有恶弱之人往甘州、肃州境内偷劫,已命诸处小镇严加捉禁”②,这样的理解与解释自相矛盾。
仔细审读原文,笔者以为,这是一封引用书信的书信(所谓信中有信,是当时书信制度的体现,即在回信中必然要引用对方来信中的主要内容,以有针对性地答复),内容里夹杂着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书与归义军节度使的致书,但信件的主体内容应是引用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书,文中以“所云”与“又云”为引用标识,由于本件书信草稿并不完整,有残缺,所以现在看不到曹元忠回答对方来信的文字内容。至于第二段引用甘州回鹘可汗书信中“往甘州偷去”的这一矛盾问题(甘州方面不可能说往甘州去抢劫),笔者考虑到这是一封书信的草稿,草拟稿中的“甘州”很有可能是“沙州”之误写。因为从书信残存的文意逻辑关系来看,“又云”之后的内容,仍然是曹元忠引用甘州回鹘书信中的内容:得知(散乱的西州回鹘带领甘州回鹘贼人)往归义军辖境偷劫的事况,到捉到偷劫之人并枷禁,再到往(甘州辖境内)诸处发遣文帖,严令甘州回鹘部属不得向归义军辖境内偷劫,如违反必有刑宪。这些显然都是以甘州回鹘可汗的口吻回答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前面某一封信件中问责甘州回鹘往归义军辖境内偷劫之事的处理过程。这样理解才文意通顺,逻辑可信,而没有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笔者的理解和解释是,P.3272v文书草稿中大量地引用了去年(966)甘州回鹘可汗致归义军节度使书札中的内容,这都是当时书信必有的格式和程式之一,即在往来文书中要摘引前件文书中的主要内容,以利于对方进行回复。第一处是第一段中“所云”之后的内容,以“所云”为引用对方书信原文中的内容的标志:“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这是甘州回鹘可汗对归义军责问甘州回鹘偷劫归义军信息的反馈,在反馈中,甘州回鹘传递了与归义军再设盟誓,重归于好的信息。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书草稿第二段中“又云”之后的内容。以往的研究认为“又云”之后的信息既有甘州回鹘可汗的反馈信息,又有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信息。但从信息传递的逻辑来分析,笔者认为,“又云”之后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引用甘州可汗“华翰”中的内容:从“在此三五人”到“使人并总眼见”,甘州回鹘可汗首先解释了甘州回鹘部族偷劫归义军的原因(因西州回鹘离乱①,一些逃亡的西州恶弱之人勾结甘州回鹘部族,打劫归义军的人口牲畜),然后是甘州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将偷劫之人禁枷起来);从“即便发遣文帖”到“必当刑宪”,是甘州可汗所采取措施的延续:下达文告给境内诸镇,警告若再有偷劫之事,必当严惩。这一句话应该仍是甘州回鹘的信息反馈。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和论证。
首先,笔者认为:第二段后部分“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之后的文句,仍然是甘州回鹘可汗所反馈的信息,这显然是归义军节度使曾在966年致书甘州,询问归义军入京使团在凉州境内被蕃部所偷劫的情况,而甘州回鹘可汗则在书信中以归义军与凉州境域相接为由,表示甘州与此事无关,请归义军询问凉州②。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将第二段“又去年”之后的内容看作是归义军节度使反馈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主要是受文中“往甘州偷去”“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的影响。笔者的解释是,由于此件是草稿,在抄写甘州回鹘书札内容时往往会出现抄写致误的现象,因而十分怀疑文中的“甘州”当是“沙州”或“瓜州”之误写;”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一语,虽然归义军与凉州之间以甘州回鹘政权相隔,但甘州回鹘自视为独立的政权,而凉州、归义军则是称臣于中原王朝的藩属,实际上二者是相通相连的,称“接连封境”也是合理的。联系历史情境,归义军所派出的朝贡使团在往来京师的途中经常被凉州、甘州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劫掠,多见诸敦煌文献。因此P.3272v此件文书总体上反映的都是就归义军被偷劫、被劫掠之事而责问甘州,而甘州回鹘可汗对此责问予以反馈的情况,故信札中大段地引用了甘州回鹘的回复,以试图对甘州的辩解进行反击。
其次,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恰好可以验证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书信草稿内容的真实性。P.t.1189是用古藏文书写的一封书札,札末盖有一颗汉文印章“肃州之印”,匈牙利学者乌瑞将其翻译为汉文的《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使大王的请牒》。笔者认为P.t.1189藏文书札是肃州某地的官员呈给归义军节度使“大王”的,其主要内容与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中所引用的甘州回鹘书状中的内容可以互相验证:当归义军的使人到达甘州时,达头部(达怛)有地位的封臣以傲慢的口气讲话,沙州使者便转而与国王(按:当系甘州回鹘可汗)交谈,国王向其大臣梅录(按:即P.3272v中的“密六”)下了一道友好的命令,令其前来肃州,为全面签订条约[按:即P.3272v中的“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在肃州的永济(安)寺内发誓“上天的有限之地,已被鞑靼人、仲云人和回鹘人瓜分完了”。然后是有关降伏塞种人地区(按:即P.3272v中的“西州”)的匪徒(按:即P.3272v中的“恶弱之人”),捕捉两位抢劫的匪徒和有关措施的安排(按:即P.3272v中的“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①为醒目起见,笔者特列表1进行对比如下:
表1P.3272v汉文文献和P.t.1189藏文文献文本内容的对比
最后,P.3272曹元忠亲笔写在判凭空白之处的一行题记“□□□(众?)都督要两地世界久远安稳,作如此好书也”,反映P.3272v信件草稿的主要内容与甘州回鹘某部都督代回鹘可汗草拟的答复归义军书札的口气正相符合②,这里的“两地世界”,显然是指敦煌和甘州两地,所以信件以引用甘州回鹘方面书信中的内容为主,曹元忠在看到甘州回鹘可汗的答复之后,赞叹答复书信写得好,在于在答复书信中以甘州和敦煌两地的长远和平和稳定为基调,这符合两地的政治利益。
2,信件草稿中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去年写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被发现
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文中“早者,因为少有贼行,已专咨启”,表明在丁卯年(967年)之前的某年曹元忠曾经写信给甘州回鹘可汗,那么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应该与责问甘州回鹘部族率人在归义军辖境内抢劫有关。幸运的是,在敦煌出土文献里,这封信也被找到了,它就是编号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现将书信录文如下③:
元忠辄有少事须合咨闻。伏希仁私必须从允。早者,当道差亲从都头曹延定往贵道复礼,况是两地一家,并无疑阻。使人去后只务宽快,并不隄防。
去五月廿七日,从向东有贼出来,于雍归镇下煞却一人、又打将马三两匹,却往东去运。后奔赴问讯,言道:”趁逃人来”。又至六月四日,悬泉镇贼下,假作往来使人,从大道,一半乘骑,一半步行,直至城门捉将作极小口五人,亦乃奔趁相□。其贼一十八人及前件雍归镇下并是回鹘,亦称“趁逃人来”。自前或有逃人经过,只是有般次行时发书寻问。不曾队队作贼偷劫。如今道途开泰,共保一家,不期如此打劫是何名价?
又,去五月十五日被肃州家一鸡悉约作引道人,倾达堤(怛)贼一百已来,于瓜州、会稽两处同日下,打将人口及牛马。此件不忏(干)贵道人也。况且兄弟才敦恩义,永契岁寒,有此恶弱之人,不要两地世界。到日伏希兄可汗天子细与寻问勾当发遣,却是久远之恩幸矣。
今因肃州人去,谨修状起居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六月日弟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曹 元忠 状上
法藏敦煌文献P.2155文书正面为抄写的《唯识二十论序》,沙门靖迈制,《大乘庄严论序》《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文书背面首先是《驼马牛羊皮历》,其实是归义军府衙内的公文,其书写字体与正面抄写的佛经文献字体不同。公文历中有宅官宋住宁、阎文昌、曹定安、押牙王宠鸾等人名。之后便有二封书信粘在一起,书写笔迹相同,是同一人在不同时期所写:第一件为某年三月某日曹元忠的书状,从此件的口气看,像是给敦煌以东的某位藩镇官员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进贡中原时间的答复。“备认王程之尤迫,预知朝骑以有期”,希望某位眷私特宽程限,至四月上旬发遣使者经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而朝贡中央。第二件就是前录书信,是某年六月某日曹元忠写给某位“兄可汗天子”的书信。通过对P.2155文书正反面文献特征的观察,笔者有理由认为,背面的《驼马牛羊皮历》和两封书信都是敦煌官府内的留存档案(将书信的副本再抄录一份,粘连在一起,留作公文档案),后被废弃,流入敦煌地区寺院,被僧人们拿来书写佛经相关的文献。背面公文和书信的书写时间一定早于正面的佛经内容。
P.2155v书状的发件人明确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收信人并不明确,只称“可汗天子”。从书信内容中反映的地理方向和具体地名,如“从向东有贼出来”“往东去”以及雍归镇、悬泉镇、瓜州、肃州、会稽等来判断,抢劫杀人事件发生在敦煌归义军辖境(宋代的归义军只控制瓜州和沙州两地)东,即瓜州境内,则抢劫杀人的匪徒来自瓜州东边的某个藩镇,而且明确为回鹘和达怛①的贼人,那么,敦煌东边能被称“可汗天子”的,就只有9世纪末建国、屡获中原王朝册封“可汗”称号的甘州回鹘民族政权了。但对P.2155v书状中的上状对象(收件人)究竟是哪一位甘州回鹘可汗,学者们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景琼①,有的认为是顺化可汗仁裕②。陆庆夫从曹元忠的官衔③辨明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写于建隆三年(962)左右。④而据《宋史·回鹘传》《宋史·太祖纪》中建隆二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遣使进贡之事⑤,力证上状对象(收状人)非景琼可汗莫属,并解释了曹元忠称景琼可汗为“兄可汗天子”的原因,认为景琼可汗极有可能是曹元忠的姐夫。荣新江推断P.2155v第二件书信“大体写于956—963年间的某年六月,最大可能是962年的农历六月”⑥,并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关于建隆二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遣使朝献的记载,推测这位甘州回鹘可汗就是景琼。
明确了P.2155v第二件书信的发信人和收信人,信中的主要内容提到有贼人(回鹘和达但两拨贼人一共抢劫三次)杀掠敦煌归义军境内人口之事,因此,P.2155v第二件书信和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之间极可能有相关性,这早已被学者们指出,如荣新江判断“这(P.3272)是阎物成出使甘州时,带去的一封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抄本。开头所说的‘早者因少有贼行,已专咨启’,应当就是上面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所述之事”⑦,郑炳林、冯培红也指出,P.2155v《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中记归义军派曹延定到甘州充使的任务是“往贵贵道复礼”,但名为复礼,实际上却是对甘州回鹘劫掠瓜沙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进行责问⑧。笔者现用列表的方式,将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和P.2155v的二封书信中所提到的相关人物与事件进行对照比较,如表2所示:
通过对三件书信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推论:P.2155第二件书信中的内容,可以和P.3272v书信草稿中关于西州离乱贼人(P.2155中称“趁逃人来”)构召回鹘贫下贼人向瓜州抢劫人口牛马的事件对应起来。但在P.2155第二件书信中没有提到P.3272v书信草稿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966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境内被贼人劫夺朝贡物品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却
很可能与P.2155第一件中所提到的朝贡事件有因果关系(见表2中画线文字对比部分)。所以,P.3272v书信草稿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966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境内被贼人劫夺朝贡物品的事件肯定是另外一封曹元忠致甘州可汗书信里的内容,即在某年六月发生回鹘贼人抢劫事件之后,曹元忠还写过一封信件,请求甘州回鹘可汗调查这一年发生的敦煌使人在凉州境内被抢劫的事件。几个月之后,甘州回鹘可汗将这二封信里的内容一并在一封信里进行了回复,也就是P.3272v书信草稿中大段引用的甘州回鹘可汗回信中的内容。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写于某年三月的P.2155第一封书信的收信人,不大可能是甘州回鹘,而可能是丝绸之路上其他藩镇的节度使,如凉州节度使或灵州节度使。
已知P.3272v书信写于丁卯年,即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那么,P.2155v书信的内容又与之密切相关,应该是967年之前的某一年①,从二封书信的文意判断,二者应该相距不会太远,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因此,P.2155v面书信的书写时间应该在乾德四年(966)六月。笔者借助丰富的材料,将964—967年之间敦煌与甘州两地之间的通使与书信往来情况进行了仔细进行梳理和考证,以期将混乱隐晦的事件线索梳理清晰,结果如下。
据敦煌研究院藏卷、董希文藏卷和P.2629缀合的乾德二年(964)归义军《酒帐》,从964年四月起至八月之间,归义军衙内有多次招待甘州使者的支酒记录,这表明964年的正月至八月、三月至八月,有两批甘州使者先后来到沙州,并长时间逗留①。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于阗王李圣天携曹王后(曹元忠的姐姐)来到敦煌,看望已经嫁给曹元忠的于阗公主(李圣天之女)。俄藏敦煌文献《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中提到的“于阗公主”就是960年七月十五日已经出现在敦煌佛会上的于阗公主,她在964年农历九月之前已经居住在敦煌,而且由于阗来的亲信婢女员孃、祐定长期服侍。但在964年九月之后,这位于阗公主和于阗王一起返回了于阗地区。②还有一个原因是,964年八月曹元忠之子曹延禄娶妻阴氏小娘子,《新妇小娘子阴氏上于阗公主起居状》就是作为新妇的阴氏要给作为其“婆婆”的于阗公主行起居状,问候于阗公主的身体起居。甘州回鹘也因此派出使团来到敦煌,参加曹延禄的结婚典礼。所以后来曹元忠于966年五月派出亲从都头曹延定作为敦煌信使,前去答谢“复礼”,结果在路上遭遇了回鹘贼人抢劫人口和马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中记载,乾德三年(965)十二月敦煌归义军派出入京朝贡使者,从北宋京师返回敦煌的途中,可能在凉州和甘州境内被部族贼人劫掠。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四条载:乾德四年(966),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或许这些“被送达甘州”的二百余回鹘与僧人,即是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和十二月由甘州回鹘和于阗国、敦煌归义军所派遣的入京进贡使团,他们往宋廷进献佛牙、宝马等物之后返回河西走廊,结果在凉州境内被部族劫掠。因此,966年曹元忠的使团返回敦煌时,带来了甘州东边某藩镇节度使通知再次朝贡宋朝的书信,曹元忠于966年三月进行了回复,即P.2155第一件书信中提及的某东边藩镇的节度使致信曹元忠通知朝贡时间,曹元忠于966年三月回复,准备在四月上旬派出入京使团经河西走廊前往中原朝贡。
966年四月上旬归义军入京使团启程之后,五月和六月间还发生了多起回鹘人和达怛人抢劫归义军辖境内人口和马牛的案件,根本原因在于966年或之前,西域的西州回鹘政权发生内乱,大量西州回鹘人逃亡投奔甘州回鹘。所以在966年六月,曹元忠在P.2155第二封书信里致信甘州可汗,派出使人,请甘州方面调查案件,并和占据肃州的龙家部落、达怛部族几方进行共同协商,以保证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通畅和往来使团的安全,使三方(甘州回鹘、敦煌归义军、肃州民族政权)两地(甘州、敦煌)重归于好。当966年四月上旬派出的入京使团再次被抢劫的消息传回敦煌时,曹元忠于966年六月之后,再次派出信使携带书信给甘州回鹘,责问甘州回鹘可汗是否知晓归义军入京使团在凉州和甘州之间被部族贼人抢劫的事件。但是因为敦煌材料的残缺,此仅为推测,姑且存疑。推测甘州回鹘可汗在收到曹元忠的这二封书信之后,统一在一封书信里进行了答复,等这封答复的书信传递回敦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966年年终的十二月了。因此,在收到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信后,曹元忠于967年正月二十四日,再次派出以阎物成为首的甘州使团,携带P.3272v书信,前往甘州,再次商谈两地保证丝路通畅、密切相系的事宜。这就是964—967年之间,敦煌与甘州之间通使和联系的主要脉络。
那么,P.2155v第二件书信具体写于966年六月的什么时间呢?敦煌文献及敦煌莫高窟的题记里,还有一些线索可以追寻。英藏敦煌所出绘画品CH00207上有一条题记,表明在966年五月九日至六月二日期间,曹元忠及其夫人曾巡礼莫高窟,并兴工修建北大像弥勒佛,一直到六月四日才返回沙州城。所以,只有在966年六月四日以后,曹元忠才有可能草拟答复甘州回鹘的P.2155v第二封书信。而甘州回鹘最后一次抢劫归义军人马的时间是六月四日,这个消息从瓜州报告传到曹元忠那里,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早就超过了六月四日。因此,P.2155背第二封书信书写的具体时间应该在六月中下旬左右。
二
由于甘州回鹘地处丝绸之路敦煌通往中原腹地的交通要道,对归义军政权而言,甘州回鹘政权有如一枚扎在归义军政权血管里的刺,时刻紧扼着归义军政权的命脉——通往东边的交通道路的通畅。故曹元忠在为敦煌归义节度使的三十年内,将甘州回鹘视为归义军辖境东边最危险而强大的敌人,无时无刻不保持警惕。但曹元忠十分注意吸取张承奉金山国时代和其父曹议金时代及其兄曹元德率军主动进攻甘州回鹘、曹元深以外交手段成功打通甘州阻绝道路的正反两方面对抗甘州回鹘的政治策略与政治经验,总体上对甘州回鹘采取守势以自保,而不是以军事挑战为主;同时,通过政治联姻的形式积极争取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于阗国为军事同盟,以加强抗衡甘州回鹘的势力。
五代末期到宋初的一段时间内,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势力的衰落和于阗国在西域势力的勃兴,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出现了复杂的政治争夺;乾德年间西州回鹘政权的崩溃更是加剧了河西走廊内的动荡和混乱,抢劫事件多次发生。西州回鹘本是西迁回鹘中的一支,在首领仆固俊的领导下,于多民族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在唐代末年,一度依附于归义军政权。在五代时期,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民族联合政权。《宋史·高昌传》中载,西州境内的民族有突厥、众熨(仲云)、样磨等十几种,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族。西州回鹘的势力主要在西州、北庭,并向西发展,到达龟兹。宋初建隆三年,西州回鹘曾遣使向宋廷进贡。直到乾德三年,还曾派遣僧人贡献佛牙。但此后,西州回鹘发生内乱,一部分部落投奔与其同种族的、强大的甘州回鹘。内乱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一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81),阿厮兰汗自称西州外生(甥)师(狮)子王,重新统一了分裂的部族,西州民族联合政权才渐稳定,对宋辽皆称臣。宋朝遣王延德出使西州,见《使高昌行记》。①因此,宋朝建立初年的一段时期内,河西走廊内动荡不安,为了保证丝路的通畅和政权的安全稳定,敦煌的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多次互相派出信使,密切联系,以达成三方两地的政治和平与稳定。两件残缺不全的出土敦煌文书P.2155v书信与P.3272书信草稿之间的紧密关联,反映了966—967年敦煌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形势。显示了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之间明争暗斗的政治关系,呈现了宋初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政治生态。其间的历史细节信息,依然值得读史者思索与体味。
关于甘州回鹘的建立始末及甘州回鹘可汗的世次,历来中外学者们研究较多①,经过学者们对传世文献的钩稽考证,其民族政权的建立过程和可汗的世次,基本上清晰地显现出来,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和方便。甘州回鹘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一直也是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关于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关系的研究上,多是对敦煌出土文献里的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于阗文文献进行综合对照,研究的方法和角度越来越呈现出文本细读、材料验证的特征。尽管如此,可其中的一些史事并不鲜明,细节也未完全呈现出来,主要还是文献不足的缘故。笔者以往来于甘州回鹘和敦煌归义军二大政权之间的信使为切入点,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的书信文献的文本细读,管窥宋初沙州和甘州二地之间的通使和联系,以深入探究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关系,从而呈现出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政治生态。
一
从公元9世纪末期甘州回鹘建立胡汉联合政权(即少数回鹘贵族统治绝大多数胡汉民众的联合政权)之日起,甘州回鹘政权就将自己的政权定位为同中原藩镇同等,甚至与周边藩镇割据力量互不统属、军事独立、地位平等的地方藩镇政权,并沿着河西走廊不断向西发展,试图控制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县)、沙州(今甘肃敦煌),进而将整个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控制起来。甘州回鹘在政治上通过朝贡中原王朝,获得中原王朝册封,以承认其政治权力;经济上挟地理之利,与中原王朝、周边藩镇进行货物贸易,影响遍及瓜、沙、于阗等地;军事上凭借优越的骑兵横行河西走廊,对归义军及其他藩镇虎视眈眈,最具军事威胁。
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之间主要是朝贡关系,还有短时期内向唐王朝请求下嫁公主的联姻关系,“除了是继承唐代回鹘与唐王朝甥舅关系的余绪之外,更主要的是使甘州回鹘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支持”①,但中央王朝却将甘州回鹘视为蕃夷和外属。就河西走廊内的藩镇割据势力而言,如河西走廊东段的灵州、凉州等藩镇,西边的归义军藩镇,都将甘州回鹘视为一“道”猃狁。唐末存续下来的藩镇格局关系,尤其是经过中原王朝对甘州回鹘的册封确认之后便固定下来。为甘州回鹘政权与周边藩镇的政治关系奠定了基调,即灵州、凉州、甘州、沙州之间,都是政治地位平等的藩镇关系,而不是政治依附的关系。既然是政治地位平等的藩镇,就存在争夺整个河西走廊控制权的矛盾,因此,在唐末到五代的七十余年间,甘州回鹘凭借切断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道路的优势,积极向西发展势力,吞并了原由敦煌归义军政权控制的肃州,并一度使归义军政权臣服,签订城下之盟。归义军政权一方面不得不主动向甘州回鹘请求下嫁公主以联姻,试图再次打通与中原王朝之间朝贡的交通道路和政治联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政权的安全,也主动与西域的于闻政权进行三次政治联姻,以抗衡甘州回鹘。②联姻与斗争,吞并与反吞并,就成为敦煌与甘州二地政权之间政治关系的一个基调,而最能反映二地之间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的,就是敦煌出土文献里奔走于两地的信使,以及这些信使们传递的信件里透露出来的细节信息。
公元960年,中原宋朝建立之后,敦煌归义军依托与于阗政权之间的亲密联姻关系积极地向刚刚建立的北宋朝廷朝贡,希望重新建立丝绸之路上的传统政治依附关系。962年正月,敦煌归义军将领曹元忠被宋朝廷正式授予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中书令的官衔,归义军得到中原王朝的直接政治支持,使自五代后周以来一度十分紧张的甘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归义军之间的政治关系趋于和缓,而且成为兄弟关系,往来通使不断。笔者通过深入挖掘文献细节,认为促成甘沙关系缓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962年,曹元忠在得到宋朝的官告之后娶于阗王李圣天和非曹夫人所生之女(于阗公主)为妻,敦煌与于阗二地之间形成了第二次政治联姻关系。①这样,曹元忠与于阗王李圣天之间结成了既是郎舅、又是子婿一岳父的双重姻亲关系。这种双重姻亲关系,正是归义军政权联合于阗对抗甘州回鹘政权,重新打开通向中原朝廷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安全保障。962—964年,是沙州、甘州和于阗三地之间的“蜜月期”,双方通使不断,但随着964年九月之后于阗公主和于阗王一起返回于阗,966年于阗王李圣天去世,于阗和敦煌二地之间的政治联姻出现了中断,甘州与沙州的政治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965—967年是河西走廊的多事之秋,西州回鹘政权崩溃,河西民族矛盾交织,甘州和敦煌之间数次通使往来,这些信使传递双方的政治意图,以解决政治纠纷。最有名的一封书信写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是归义军曹元忠派使头阎物成出使甘州,其携带的亲笔信件。从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②,可知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因为甘州回鹘偷劫归义军使人而责难问讯,双方书札往复频繁的情形。
1.信件的书写年代、性质、主要内容和信使
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③
早者,因为有少贼行,已专咨启。近蒙华翰,兼惠厚仪,无任感钦之至。所云:“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闻此嘉言,倍深感仰。况厶忝为眷爱,实惬衷诚。永敦久远之情,固保始终之契。
又云:“在此三五人,往贵道偷来之事况,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厶并不知闻。近者示及,方知子(仔)细。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诸)处官人,必当刑宪!’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人总并散,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劫去)玉□□□,至凉州寻问即是!”(后缺)
上述书信写于丁卯年正月,那么丁卯年是哪一年呢?根据敦煌文献的出土年代,可能是公元907年(唐天祐四年)、967年(宋乾德五年)、1027年(宋天圣五年)中的某一个,根据文献上的其他情况(详见下文)来判断,显然967年最为合适。从书信草稿内容来判断,应当是敦煌地方官给甘州地方官的书信草稿,所以带有草稿涂抹的特征。
由于《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是一封书信的草稿,因此有许多让人困惑而容易理解歧误的地方。比如,发信人和收信人分别是谁呢?对此,有极少意见将其理解为甘州使头代表归义军节度使给甘州回鹘的书信,如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①一文中提到,归义军通
使甘州回鹘时,归义军“专门设立甘州使头以分管甘州使团事宜”,认为甘州使头处理邦交事务,责关重大,因此享有很大的权力,故将P.3272v文书视为甘州使头致回鹘可汗的书状,是甘州使头代表归义军节度使在与甘州可汗进行邦交谈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中认为“此件,由内容看,系致甘州回鹘书”②,但未指出发件人为谁。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这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草稿③。陆庆夫进一步更将P.2155v文书与P.3272v文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关联密切,都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曹元忠姐夫)的书状④。敦煌文献及传世文献显示,967年(宋乾德五年)任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人正是曹元忠。那么,这封书信非常可能就是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名义草拟的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草稿,故称“书本”,本即草稿之意。草稿拟好之后,拟由归义军派出的使头阎物成传递至甘州。书信草稿的正面是丙寅年正月、二月的牧羊人兀宁牒状二件,上有大字的判凭“为凭”及鸟形押,书写的文字特征及鸟形押的类型与曹元忠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的类型十分相近。因此,背面丁卯年的书信草稿应该与正面丙寅年的文书年代十分相近,由于丙寅年之后便是丁卯年,所以,这显然是利用丙寅年存档(为凭证)旧文书的背面起草了书信草稿,丙寅年是公元966年,中原年号是北宋乾德四年。
搞清楚了P.3272v文书的年代、性质和收发对象之后,文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由于书信格式较为特殊,学者们对内容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种意见认为,文中既有甘州回鹘可汗回敦煌曹元忠上一封书信的答书,即书信草稿文中第一段第二行“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的内容,反映甘州与属下各部设盟立誓,不许侵扰归义军境界⑤;也有曹元忠回答甘州回鹘可汗来信中的内容,即书信草稿第二段第四行“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处官人,必当刑宪”⑥,故将文中“又云”部分的内容全部视为曹元忠致书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李正宇先生也持此种观点。在《敦煌学导论》一书附录的《敦煌文献选讲》中,李正宇将P.3272v文书解读为“北宋乾德五年(967)沙州归义军遣使送交甘州回鹘的公文。(公文)内容反映了各自境内不法之徒前往对方境内劫掠以及两邦首脑互相谅解,各自约束本邦以保持友好关系的史实”①,但细读书信内容,如果将第二段“又云”之后的内容理解为曹元忠书信里的内容,显然与文意不合。但如果不这样理解,又与后文的“甘州”二字相矛盾,所以李正宇不得不将后文中的“小镇”解释为“归义军境内负责军事戍守及社会治安的军镇”,是归义军节度使“告知(甘州)近来西州离乱,有恶弱之人往甘州、肃州境内偷劫,已命诸处小镇严加捉禁”②,这样的理解与解释自相矛盾。
仔细审读原文,笔者以为,这是一封引用书信的书信(所谓信中有信,是当时书信制度的体现,即在回信中必然要引用对方来信中的主要内容,以有针对性地答复),内容里夹杂着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书与归义军节度使的致书,但信件的主体内容应是引用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书,文中以“所云”与“又云”为引用标识,由于本件书信草稿并不完整,有残缺,所以现在看不到曹元忠回答对方来信的文字内容。至于第二段引用甘州回鹘可汗书信中“往甘州偷去”的这一矛盾问题(甘州方面不可能说往甘州去抢劫),笔者考虑到这是一封书信的草稿,草拟稿中的“甘州”很有可能是“沙州”之误写。因为从书信残存的文意逻辑关系来看,“又云”之后的内容,仍然是曹元忠引用甘州回鹘书信中的内容:得知(散乱的西州回鹘带领甘州回鹘贼人)往归义军辖境偷劫的事况,到捉到偷劫之人并枷禁,再到往(甘州辖境内)诸处发遣文帖,严令甘州回鹘部属不得向归义军辖境内偷劫,如违反必有刑宪。这些显然都是以甘州回鹘可汗的口吻回答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前面某一封信件中问责甘州回鹘往归义军辖境内偷劫之事的处理过程。这样理解才文意通顺,逻辑可信,而没有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笔者的理解和解释是,P.3272v文书草稿中大量地引用了去年(966)甘州回鹘可汗致归义军节度使书札中的内容,这都是当时书信必有的格式和程式之一,即在往来文书中要摘引前件文书中的主要内容,以利于对方进行回复。第一处是第一段中“所云”之后的内容,以“所云”为引用对方书信原文中的内容的标志:“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这是甘州回鹘可汗对归义军责问甘州回鹘偷劫归义军信息的反馈,在反馈中,甘州回鹘传递了与归义军再设盟誓,重归于好的信息。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书草稿第二段中“又云”之后的内容。以往的研究认为“又云”之后的信息既有甘州回鹘可汗的反馈信息,又有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信息。但从信息传递的逻辑来分析,笔者认为,“又云”之后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引用甘州可汗“华翰”中的内容:从“在此三五人”到“使人并总眼见”,甘州回鹘可汗首先解释了甘州回鹘部族偷劫归义军的原因(因西州回鹘离乱①,一些逃亡的西州恶弱之人勾结甘州回鹘部族,打劫归义军的人口牲畜),然后是甘州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将偷劫之人禁枷起来);从“即便发遣文帖”到“必当刑宪”,是甘州可汗所采取措施的延续:下达文告给境内诸镇,警告若再有偷劫之事,必当严惩。这一句话应该仍是甘州回鹘的信息反馈。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和论证。
首先,笔者认为:第二段后部分“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之后的文句,仍然是甘州回鹘可汗所反馈的信息,这显然是归义军节度使曾在966年致书甘州,询问归义军入京使团在凉州境内被蕃部所偷劫的情况,而甘州回鹘可汗则在书信中以归义军与凉州境域相接为由,表示甘州与此事无关,请归义军询问凉州②。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将第二段“又去年”之后的内容看作是归义军节度使反馈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主要是受文中“往甘州偷去”“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的影响。笔者的解释是,由于此件是草稿,在抄写甘州回鹘书札内容时往往会出现抄写致误的现象,因而十分怀疑文中的“甘州”当是“沙州”或“瓜州”之误写;”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一语,虽然归义军与凉州之间以甘州回鹘政权相隔,但甘州回鹘自视为独立的政权,而凉州、归义军则是称臣于中原王朝的藩属,实际上二者是相通相连的,称“接连封境”也是合理的。联系历史情境,归义军所派出的朝贡使团在往来京师的途中经常被凉州、甘州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劫掠,多见诸敦煌文献。因此P.3272v此件文书总体上反映的都是就归义军被偷劫、被劫掠之事而责问甘州,而甘州回鹘可汗对此责问予以反馈的情况,故信札中大段地引用了甘州回鹘的回复,以试图对甘州的辩解进行反击。
其次,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恰好可以验证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书信草稿内容的真实性。P.t.1189是用古藏文书写的一封书札,札末盖有一颗汉文印章“肃州之印”,匈牙利学者乌瑞将其翻译为汉文的《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使大王的请牒》。笔者认为P.t.1189藏文书札是肃州某地的官员呈给归义军节度使“大王”的,其主要内容与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中所引用的甘州回鹘书状中的内容可以互相验证:当归义军的使人到达甘州时,达头部(达怛)有地位的封臣以傲慢的口气讲话,沙州使者便转而与国王(按:当系甘州回鹘可汗)交谈,国王向其大臣梅录(按:即P.3272v中的“密六”)下了一道友好的命令,令其前来肃州,为全面签订条约[按:即P.3272v中的“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在肃州的永济(安)寺内发誓“上天的有限之地,已被鞑靼人、仲云人和回鹘人瓜分完了”。然后是有关降伏塞种人地区(按:即P.3272v中的“西州”)的匪徒(按:即P.3272v中的“恶弱之人”),捕捉两位抢劫的匪徒和有关措施的安排(按:即P.3272v中的“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①为醒目起见,笔者特列表1进行对比如下:
表1P.3272v汉文文献和P.t.1189藏文文献文本内容的对比
最后,P.3272曹元忠亲笔写在判凭空白之处的一行题记“□□□(众?)都督要两地世界久远安稳,作如此好书也”,反映P.3272v信件草稿的主要内容与甘州回鹘某部都督代回鹘可汗草拟的答复归义军书札的口气正相符合②,这里的“两地世界”,显然是指敦煌和甘州两地,所以信件以引用甘州回鹘方面书信中的内容为主,曹元忠在看到甘州回鹘可汗的答复之后,赞叹答复书信写得好,在于在答复书信中以甘州和敦煌两地的长远和平和稳定为基调,这符合两地的政治利益。
2,信件草稿中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去年写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被发现
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文中“早者,因为少有贼行,已专咨启”,表明在丁卯年(967年)之前的某年曹元忠曾经写信给甘州回鹘可汗,那么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应该与责问甘州回鹘部族率人在归义军辖境内抢劫有关。幸运的是,在敦煌出土文献里,这封信也被找到了,它就是编号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现将书信录文如下③:
元忠辄有少事须合咨闻。伏希仁私必须从允。早者,当道差亲从都头曹延定往贵道复礼,况是两地一家,并无疑阻。使人去后只务宽快,并不隄防。
去五月廿七日,从向东有贼出来,于雍归镇下煞却一人、又打将马三两匹,却往东去运。后奔赴问讯,言道:”趁逃人来”。又至六月四日,悬泉镇贼下,假作往来使人,从大道,一半乘骑,一半步行,直至城门捉将作极小口五人,亦乃奔趁相□。其贼一十八人及前件雍归镇下并是回鹘,亦称“趁逃人来”。自前或有逃人经过,只是有般次行时发书寻问。不曾队队作贼偷劫。如今道途开泰,共保一家,不期如此打劫是何名价?
又,去五月十五日被肃州家一鸡悉约作引道人,倾达堤(怛)贼一百已来,于瓜州、会稽两处同日下,打将人口及牛马。此件不忏(干)贵道人也。况且兄弟才敦恩义,永契岁寒,有此恶弱之人,不要两地世界。到日伏希兄可汗天子细与寻问勾当发遣,却是久远之恩幸矣。
今因肃州人去,谨修状起居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六月日弟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曹 元忠 状上
法藏敦煌文献P.2155文书正面为抄写的《唯识二十论序》,沙门靖迈制,《大乘庄严论序》《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文书背面首先是《驼马牛羊皮历》,其实是归义军府衙内的公文,其书写字体与正面抄写的佛经文献字体不同。公文历中有宅官宋住宁、阎文昌、曹定安、押牙王宠鸾等人名。之后便有二封书信粘在一起,书写笔迹相同,是同一人在不同时期所写:第一件为某年三月某日曹元忠的书状,从此件的口气看,像是给敦煌以东的某位藩镇官员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进贡中原时间的答复。“备认王程之尤迫,预知朝骑以有期”,希望某位眷私特宽程限,至四月上旬发遣使者经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而朝贡中央。第二件就是前录书信,是某年六月某日曹元忠写给某位“兄可汗天子”的书信。通过对P.2155文书正反面文献特征的观察,笔者有理由认为,背面的《驼马牛羊皮历》和两封书信都是敦煌官府内的留存档案(将书信的副本再抄录一份,粘连在一起,留作公文档案),后被废弃,流入敦煌地区寺院,被僧人们拿来书写佛经相关的文献。背面公文和书信的书写时间一定早于正面的佛经内容。
P.2155v书状的发件人明确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收信人并不明确,只称“可汗天子”。从书信内容中反映的地理方向和具体地名,如“从向东有贼出来”“往东去”以及雍归镇、悬泉镇、瓜州、肃州、会稽等来判断,抢劫杀人事件发生在敦煌归义军辖境(宋代的归义军只控制瓜州和沙州两地)东,即瓜州境内,则抢劫杀人的匪徒来自瓜州东边的某个藩镇,而且明确为回鹘和达怛①的贼人,那么,敦煌东边能被称“可汗天子”的,就只有9世纪末建国、屡获中原王朝册封“可汗”称号的甘州回鹘民族政权了。但对P.2155v书状中的上状对象(收件人)究竟是哪一位甘州回鹘可汗,学者们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景琼①,有的认为是顺化可汗仁裕②。陆庆夫从曹元忠的官衔③辨明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写于建隆三年(962)左右。④而据《宋史·回鹘传》《宋史·太祖纪》中建隆二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遣使进贡之事⑤,力证上状对象(收状人)非景琼可汗莫属,并解释了曹元忠称景琼可汗为“兄可汗天子”的原因,认为景琼可汗极有可能是曹元忠的姐夫。荣新江推断P.2155v第二件书信“大体写于956—963年间的某年六月,最大可能是962年的农历六月”⑥,并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关于建隆二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遣使朝献的记载,推测这位甘州回鹘可汗就是景琼。
明确了P.2155v第二件书信的发信人和收信人,信中的主要内容提到有贼人(回鹘和达但两拨贼人一共抢劫三次)杀掠敦煌归义军境内人口之事,因此,P.2155v第二件书信和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之间极可能有相关性,这早已被学者们指出,如荣新江判断“这(P.3272)是阎物成出使甘州时,带去的一封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抄本。开头所说的‘早者因少有贼行,已专咨启’,应当就是上面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所述之事”⑦,郑炳林、冯培红也指出,P.2155v《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中记归义军派曹延定到甘州充使的任务是“往贵贵道复礼”,但名为复礼,实际上却是对甘州回鹘劫掠瓜沙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进行责问⑧。笔者现用列表的方式,将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和P.2155v的二封书信中所提到的相关人物与事件进行对照比较,如表2所示:
通过对三件书信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推论:P.2155第二件书信中的内容,可以和P.3272v书信草稿中关于西州离乱贼人(P.2155中称“趁逃人来”)构召回鹘贫下贼人向瓜州抢劫人口牛马的事件对应起来。但在P.2155第二件书信中没有提到P.3272v书信草稿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966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境内被贼人劫夺朝贡物品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却
很可能与P.2155第一件中所提到的朝贡事件有因果关系(见表2中画线文字对比部分)。所以,P.3272v书信草稿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966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境内被贼人劫夺朝贡物品的事件肯定是另外一封曹元忠致甘州可汗书信里的内容,即在某年六月发生回鹘贼人抢劫事件之后,曹元忠还写过一封信件,请求甘州回鹘可汗调查这一年发生的敦煌使人在凉州境内被抢劫的事件。几个月之后,甘州回鹘可汗将这二封信里的内容一并在一封信里进行了回复,也就是P.3272v书信草稿中大段引用的甘州回鹘可汗回信中的内容。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写于某年三月的P.2155第一封书信的收信人,不大可能是甘州回鹘,而可能是丝绸之路上其他藩镇的节度使,如凉州节度使或灵州节度使。
已知P.3272v书信写于丁卯年,即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那么,P.2155v书信的内容又与之密切相关,应该是967年之前的某一年①,从二封书信的文意判断,二者应该相距不会太远,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因此,P.2155v面书信的书写时间应该在乾德四年(966)六月。笔者借助丰富的材料,将964—967年之间敦煌与甘州两地之间的通使与书信往来情况进行了仔细进行梳理和考证,以期将混乱隐晦的事件线索梳理清晰,结果如下。
据敦煌研究院藏卷、董希文藏卷和P.2629缀合的乾德二年(964)归义军《酒帐》,从964年四月起至八月之间,归义军衙内有多次招待甘州使者的支酒记录,这表明964年的正月至八月、三月至八月,有两批甘州使者先后来到沙州,并长时间逗留①。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于阗王李圣天携曹王后(曹元忠的姐姐)来到敦煌,看望已经嫁给曹元忠的于阗公主(李圣天之女)。俄藏敦煌文献《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中提到的“于阗公主”就是960年七月十五日已经出现在敦煌佛会上的于阗公主,她在964年农历九月之前已经居住在敦煌,而且由于阗来的亲信婢女员孃、祐定长期服侍。但在964年九月之后,这位于阗公主和于阗王一起返回了于阗地区。②还有一个原因是,964年八月曹元忠之子曹延禄娶妻阴氏小娘子,《新妇小娘子阴氏上于阗公主起居状》就是作为新妇的阴氏要给作为其“婆婆”的于阗公主行起居状,问候于阗公主的身体起居。甘州回鹘也因此派出使团来到敦煌,参加曹延禄的结婚典礼。所以后来曹元忠于966年五月派出亲从都头曹延定作为敦煌信使,前去答谢“复礼”,结果在路上遭遇了回鹘贼人抢劫人口和马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中记载,乾德三年(965)十二月敦煌归义军派出入京朝贡使者,从北宋京师返回敦煌的途中,可能在凉州和甘州境内被部族贼人劫掠。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四条载:乾德四年(966),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或许这些“被送达甘州”的二百余回鹘与僧人,即是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和十二月由甘州回鹘和于阗国、敦煌归义军所派遣的入京进贡使团,他们往宋廷进献佛牙、宝马等物之后返回河西走廊,结果在凉州境内被部族劫掠。因此,966年曹元忠的使团返回敦煌时,带来了甘州东边某藩镇节度使通知再次朝贡宋朝的书信,曹元忠于966年三月进行了回复,即P.2155第一件书信中提及的某东边藩镇的节度使致信曹元忠通知朝贡时间,曹元忠于966年三月回复,准备在四月上旬派出入京使团经河西走廊前往中原朝贡。
966年四月上旬归义军入京使团启程之后,五月和六月间还发生了多起回鹘人和达怛人抢劫归义军辖境内人口和马牛的案件,根本原因在于966年或之前,西域的西州回鹘政权发生内乱,大量西州回鹘人逃亡投奔甘州回鹘。所以在966年六月,曹元忠在P.2155第二封书信里致信甘州可汗,派出使人,请甘州方面调查案件,并和占据肃州的龙家部落、达怛部族几方进行共同协商,以保证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通畅和往来使团的安全,使三方(甘州回鹘、敦煌归义军、肃州民族政权)两地(甘州、敦煌)重归于好。当966年四月上旬派出的入京使团再次被抢劫的消息传回敦煌时,曹元忠于966年六月之后,再次派出信使携带书信给甘州回鹘,责问甘州回鹘可汗是否知晓归义军入京使团在凉州和甘州之间被部族贼人抢劫的事件。但是因为敦煌材料的残缺,此仅为推测,姑且存疑。推测甘州回鹘可汗在收到曹元忠的这二封书信之后,统一在一封书信里进行了答复,等这封答复的书信传递回敦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966年年终的十二月了。因此,在收到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信后,曹元忠于967年正月二十四日,再次派出以阎物成为首的甘州使团,携带P.3272v书信,前往甘州,再次商谈两地保证丝路通畅、密切相系的事宜。这就是964—967年之间,敦煌与甘州之间通使和联系的主要脉络。
那么,P.2155v第二件书信具体写于966年六月的什么时间呢?敦煌文献及敦煌莫高窟的题记里,还有一些线索可以追寻。英藏敦煌所出绘画品CH00207上有一条题记,表明在966年五月九日至六月二日期间,曹元忠及其夫人曾巡礼莫高窟,并兴工修建北大像弥勒佛,一直到六月四日才返回沙州城。所以,只有在966年六月四日以后,曹元忠才有可能草拟答复甘州回鹘的P.2155v第二封书信。而甘州回鹘最后一次抢劫归义军人马的时间是六月四日,这个消息从瓜州报告传到曹元忠那里,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早就超过了六月四日。因此,P.2155背第二封书信书写的具体时间应该在六月中下旬左右。
二
由于甘州回鹘地处丝绸之路敦煌通往中原腹地的交通要道,对归义军政权而言,甘州回鹘政权有如一枚扎在归义军政权血管里的刺,时刻紧扼着归义军政权的命脉——通往东边的交通道路的通畅。故曹元忠在为敦煌归义节度使的三十年内,将甘州回鹘视为归义军辖境东边最危险而强大的敌人,无时无刻不保持警惕。但曹元忠十分注意吸取张承奉金山国时代和其父曹议金时代及其兄曹元德率军主动进攻甘州回鹘、曹元深以外交手段成功打通甘州阻绝道路的正反两方面对抗甘州回鹘的政治策略与政治经验,总体上对甘州回鹘采取守势以自保,而不是以军事挑战为主;同时,通过政治联姻的形式积极争取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于阗国为军事同盟,以加强抗衡甘州回鹘的势力。
五代末期到宋初的一段时间内,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势力的衰落和于阗国在西域势力的勃兴,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出现了复杂的政治争夺;乾德年间西州回鹘政权的崩溃更是加剧了河西走廊内的动荡和混乱,抢劫事件多次发生。西州回鹘本是西迁回鹘中的一支,在首领仆固俊的领导下,于多民族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在唐代末年,一度依附于归义军政权。在五代时期,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民族联合政权。《宋史·高昌传》中载,西州境内的民族有突厥、众熨(仲云)、样磨等十几种,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族。西州回鹘的势力主要在西州、北庭,并向西发展,到达龟兹。宋初建隆三年,西州回鹘曾遣使向宋廷进贡。直到乾德三年,还曾派遣僧人贡献佛牙。但此后,西州回鹘发生内乱,一部分部落投奔与其同种族的、强大的甘州回鹘。内乱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一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81),阿厮兰汗自称西州外生(甥)师(狮)子王,重新统一了分裂的部族,西州民族联合政权才渐稳定,对宋辽皆称臣。宋朝遣王延德出使西州,见《使高昌行记》。①因此,宋朝建立初年的一段时期内,河西走廊内动荡不安,为了保证丝路的通畅和政权的安全稳定,敦煌的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多次互相派出信使,密切联系,以达成三方两地的政治和平与稳定。两件残缺不全的出土敦煌文书P.2155v书信与P.3272书信草稿之间的紧密关联,反映了966—967年敦煌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形势。显示了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之间明争暗斗的政治关系,呈现了宋初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政治生态。其间的历史细节信息,依然值得读史者思索与体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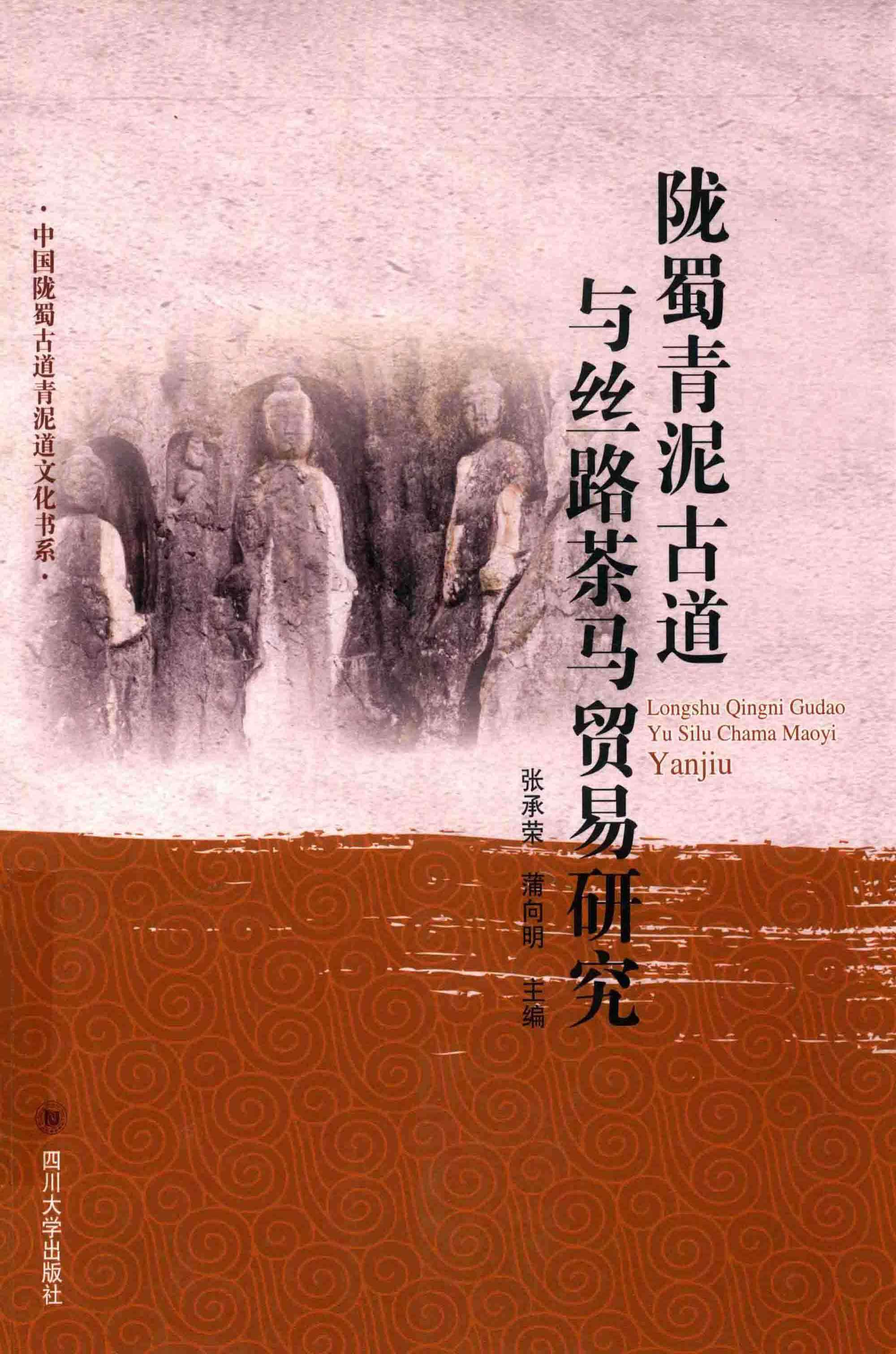
《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丝绸之路与陇蜀青泥古道”“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蜀道申遗与陇蜀秦蜀交通”“青泥古道与陇南地域文化”四部分,是近年来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陇南本土在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重点在陇蜀青泥古道自汉唐以来政治、军事、交通、商贸诸方面的文化研究,兼顾青泥道在丝绸之路茶马贸易方面的历史地位、历史文献、文化遗存以及沟通南北丝绸之路廊道路网方面的研究。
阅读
相关人物
王使臻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