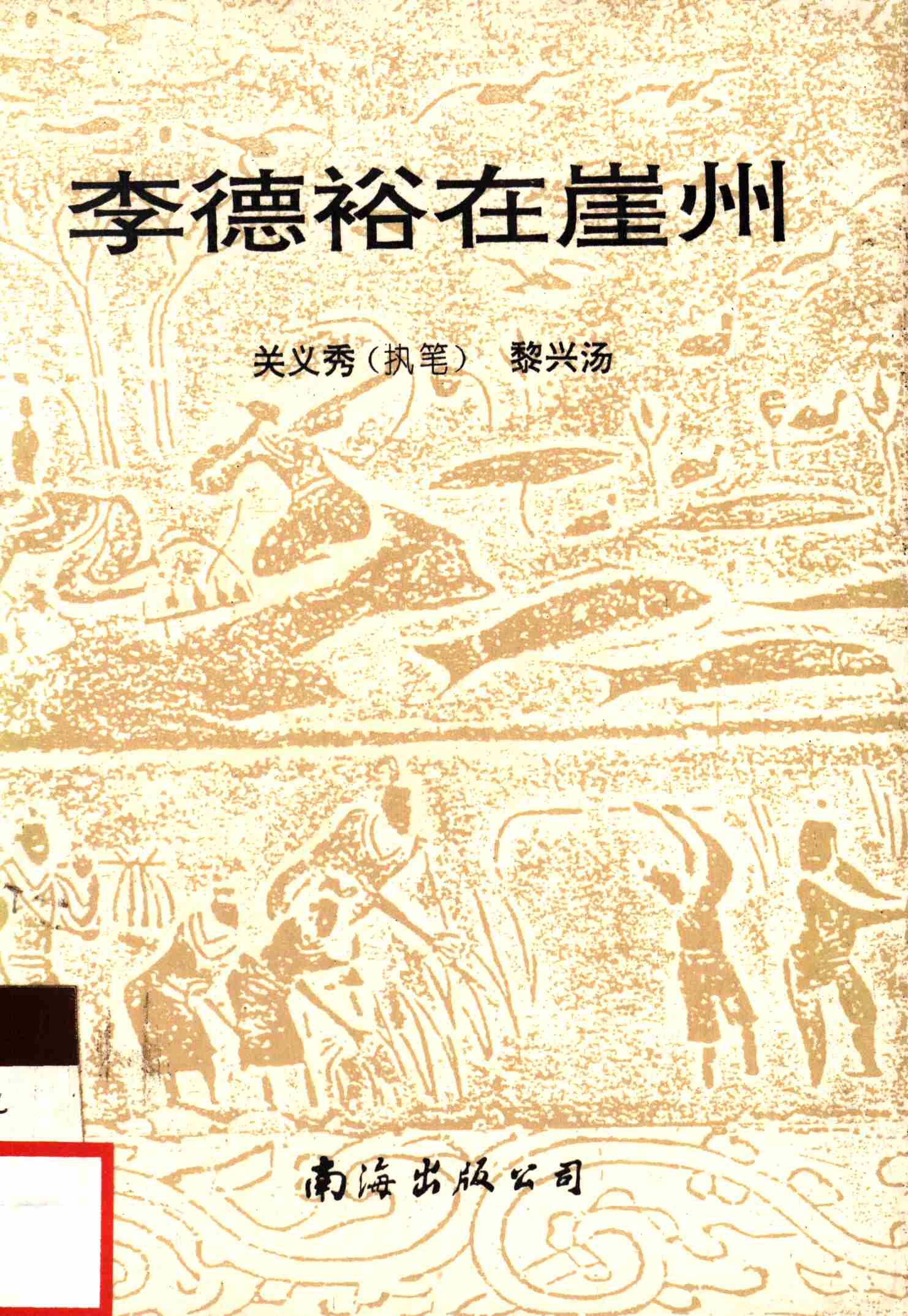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骄阳,烤熟了深山里一个金秋。
远处,那一片苍黑的林子里,荔枝树上挂满一串串酡红的荔枝果;近处,翠绿的山坡上,山柚果熟了,桃金娘熟了,野芭蕉熟了,绿丛间点缀着嫣紫嫩黄。松鼠们、野鸡们窜来窜去,上飞下跳,忙碌地消受着秋天的馈赠。
抱班寨里头次种下水稻,就获得好收成。村头寨尾人们相遇了,便要停下来嘀咕一番。明知道对方家里稻谷成堆,偏要问今年收成不赖吧;明明是心里乐开了花,却发愁说缺了个大谷围。这个说天开了眼,那个说帅公来得好,于是一齐眉开眼笑,忙坏了腰。
夕阳快下山了,秋玉还在场上槌着谷子。她槌着槌着,却忍不住放下木棒,撮一撮黄澄澄的谷子放在掌心里,捻来捏去,啧啧地赞不绝口,“多好的谷子!阿爹,你来看看!”
“傻孩子,你说过几遍了?阿爹看了十次八次罗!”帕威笑嘻嘻的,“乖孩子,谷子都填进腹里,饱啦?还不快吃饭!”
“阿爹,你儿时请李大人来尝新?人家不来,谷子该不会从天上飞下来吧!”秋王咂咂嘴。
“那当然,当然,要请李大人尝新!”帕威点点头,突然叹了叹气,“咱只怕——”
“怕什么?”秋玉吃了一惊。
“只怕明年李大人……他他要回京城罗!”帕威瞧女儿那副模样,第一次撒起谎来。
“不会的,不会的!阿爹,你胡说……李大人的家不是在在这……”秋玉一听失了神,傻乎乎的,脸也刹时惨白。
帕威可吓坏了。他连忙扶起秋玉,一遍一遍咒骂自己,象哄小孩似的哄着秋玉,“傻孩子,李大人真要走,咱也会拉住他!李大人早说过,真让他回去当皇帝,他也不走了!”这后一句,其实是帕威给女儿定心丸吃,故意编出来的。
秋玉这才破涕为笑。她收工吃过晚饭,又忐忑不安起来,勿勿回到寮房。
月亮升起了。
蓝天里悬着一面玉镜,屋前一汪清水潭里也闪动一面玉镜。多少个花月夜,秋玉曾对着它,照一照姣好的脸蛋,阿光也曾对着它,照一照英武的身影,然后,才双双走向蓝幽幽的小路。那时,月光是粉,匀匀地筛下来,往她脸上撒上薄粉,着上淡装,把她打扮成一个玉女。那时,月光是水,把层峦叠嶂洗得象一堆堆翡翠,把半腹子愁烦洗净,只剩下柔肠七尺,七尺柔肠。后来,阿光撇下她走了。她也曾想跟阿光一道去了,后来则想这辈子孤单一人活下去。不管怎么说,这一汪水潭近在咫尺,她从那时起就躲着它,白天夜里都躲着它。然而,今晚秋玉躺在床上,却无法宁静思绪。她身不由己,走出房外,走到清水潭边,依然倚靠在那株菠萝蜜树上……
一会儿,传来了唎咧的声音,那跳荡着欢乐,跳荡着激情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秋玉突然转过身,走回寮房,蒙起被子躺下,一头嘟哝着,“烦死人了!”
这时,多情的歌儿飞进寮房:
想死你呀好妹妹,
想到石头上开花,
想到马儿长出角,
想到树皮不生麻……
真想灌你迷魂药呀,
我的好妹妹!
秋玉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她分不清是无奈还是应酬,是绝望还是企盼,到底是掀开被子,在床上翻过身,叹了叹气,这才一骨碌爬起。
几个英俊的小伙子走到门口外边。人未进门,歌儿先闯进门口:
妹妹的寮宽房又宽,
妹妹的竹床凉又凉。
哥想坐到侬身边,
只求妹妹把口张。
秋玉款款起身,搬过板凳,排上几口槟榔,请客人尝尝,请客人赏光,然后,慢慢唱了起来:
哥哥有心来相伴,
妹妹有心也枉闲。
屋前花株已有主,
一花难得两家栽。
此处不卖别处买,
东市无鱼走西海。
有志打石石都开,
何愁不得好花栽。
秋玉委婉地把向她求爱的小伙子打发走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夜、两夜的事情。然而,人走了,那悠悠的口弓声、鼻箫声,似乎还回荡在屋子里面。此刻,那声音就是蜿蜒的青溪,而她一颗心就是青溪底部晶莹的卵石,任着流水冲刷,冲出了怅惘,冲出了苦涩,冲出了焦灼的渴望。秋玉兀自苦笑着,咱这株花有主,那末,主是谁呢?咱为啥要对人家说谎呢?她痛苦地闭上眼睛,朦胧中分明有谁走来,那样面熟,却又那样陌生。对了,他是咱的“主”,快挽住他,别让他跑掉。秋玉不觉叫出声来,睁开眼睛,床上人单影独,屋外也只有清冷的月影。她觉得无边的失落,倚在门上怅然而望。她多么想见到那桔黄色的灯光见到那梦中常常出现的身影!然而,那灯光,那身影,都被一间间船形屋挡住了。人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越发使秋玉惆怅不已。
又是一个明媚的秋日。
太阳刚爬过对面山头,帕威就请来了李德裕。他最近腌制的鹿肉茶刚开缸,自然要请李德裕品尝一番。
“大人,你慢慢地吃,慢慢喝,看咱的茶,酒蜜,比皇帝给你吃的、喝的怎么样?”帕威大献殷勤,带着二十分的期待说。
李德裕果真慢吃慢喝,不时咂一咂嘴唇,不时看一看帕威那个得意劲儿。他已明白帕威期待的是什么,却摇了摇头说,“比皇宫里吃的、喝的,差多了!”
“什么?”帕威突然沉下脸来,“咱黎家的,怎差?你不说个明白,今后咱不再请你!”
“真的?”李德裕嘿嘿笑着问。其实,李德裕逗逗他罢了。刚刚尝上茶,李德裕觉得有点腻,等到茶入肠胃,才觉得有一股清甜淡香的气味沁上喉咙,全身瞬间变得无比爽快,比宫庭佳肴胜了五分。那酒蜜更是妙不可言:起先,一丝清甜、几许香馥,透过喉咙,进入肺腑,渗入每个孔窍。以后,那香、那甜,变成发酵剂,把片刻领略到的无比快慰,酿造成韵味无穷的享受。当下,帕威生气,倒逗得他直乐。他连忙改过口来,“峒长,皇宫里的,比咱的差多了,差多了!你刚才不听明白。改日我还要给茶和酒蜜写写文章,传播出去,留给后人!”
帕威转怒为喜,一个劲儿给李德裕灌起酒来。
秋玉在一旁可急坏了。她知道李德裕酒量不大,万一喝多了,身子消受不了,就麻烦了。她几次抢过少埕子,不让帕威倒酒,可是帕威哪里肯依?此刻,他的千般情,万般意,全在酒中了。
秋玉不想让父亲扫兴,又不想让李德裕坏了身子,一时无计可施,急红了脸。幸好她脑子灵,乘着帕威不在意,捧上一碗鹧鸪茶,来了个偷梁换柱,悄悄端起李德裕面前那碗酒,“阿爹,孩子陪你们喝!”说完,她一饮而尽,才深情地对着李德裕,“李大人,该你喝了!”
李德裕一时还愣住,禁不得秋玉再三恳请,才慢慢呷了起来。才呷几口,他便觉得味道不同,热烘烘的脑门也清爽几分。他好生奇怪,直到悟出秋玉以茶代酒帮了他的忙,才叹息着,“多亏这孩子有心!”
几天过去了。秋玉织好了一张闪亮簇新的黎锦,却直盯住上面的花花草草出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想让他爹拿给李德裕,她又想亲自给他送去。可她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好办法,最后,鼓起勇气去请李德裕。
秋玉有满腹话要说,却觉得无从说起,一路走来,心里都象给猫抓一样。向阳坡上,一对班鸠扑腾扑腾着,从低枝跳上了高枝。顿时,她脸颊抹上灿灿秋光,一对乌亮的眸子闪着兴奋的光芒,连那说话的声音也格外动听,“大人,斑鸠鸟咕咕喊,它们喊的是啥呀?”
李德裕摇了摇头,饶有兴致地问,“阿玉,你就能听得出鸟的说话?”
“怎么不?”秋玉咂了咂嘴巴。
“哟,那你就说给我听听!”李德裕笑了笑。
“大人,你猜一猜罗!那只雌鸟跟着雄鸟,一步不离,它们会说什么? ”秋玉调皮地扮了一个怪相。
“它们说今天你好高兴呀!”李德裕有意逗一逗秋玉。
“大人,你又编派人了!雌的骂雄鸟……傻……”秋玉涨红了脸,不再说下去。
他们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地,秋玉的寮房出在眼前。突然,李德裕一下子敛声敛气的,刹地停住脚步。
“大人,你嫌咱这屋子小吧?”秋玉逗笑着,哪里晓得李德裕的心事!这是他同夫人生离死别之地。如今风景依旧,人事已非,当然会勾起李德裕满腔悲愤。而且,李德裕也知道,这小小草屋,是黎家子女耕耘着爱情的一块热土。它只能属于年轻一代,而他,早已是爱情青树上的一张秋后黄叶。面前那低矮的门槛,早已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台阶。当然,这一切秋玉並不是毫无所知,但多少天来,她望着李德裕孤身一人,撑住生命的小舟,她于心不忍呀,出于感激、敬仰,出于同情、怜悯,她铁定决心,想去填补李夫人空下来的位置。她认为唯有这样做,才能给李德裕最大的温暖,给她自己无边的快慰。至于面前的深谷沟壑,她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甚至根本不愿去想。这些日子,一个心底的呼唤,使她把少女的自尊都豁了出去。就是面前有火海,有刀山 她也决不犹豫、彷徨,毫无反悔地朝前走。今天,她请 李德裕前来看看黎锦,为的是好好乘机表白心迹。此刻,她可谓情迷心窍,也就不理会李德裕的心事了。
“不小……不小……”李德裕吱唔着,神态异常尴尬呆在那里不动。
秋玉慌里慌张,匆忙跑进屋里抱出来一张吉贝被,“大人,冬天快来啦。这被子,你就拿去遮遮寒吧!”
“秋玉,你的情我领了。这被子,你还是留住日后用吧!”李德裕难为情地推辞着。
“大人,你不要被子,你……你……你瞧不起咱!”秋玉噘起嘴巴,汹声汹气地说。
李德裕一愣,不由双手接过吉贝被来。一打开,双手却不停地哆嗦;他捧不住苍山碧海,捧不住顶天的石柱,捧不住成双成对的五色雀,捧不住被里包着的一条定情带!他脸色发白,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大人,你,你怎么啦?”秋玉赶忙扶住李德裕。
“我……,我……我患了风寒……会好……”李德裕结结巴巴地说。
“大人,进屋里歇息吧!咱煮药给你喝,煮热粥喂你,咱什么都愿意为你做!”秋玉喋喋不休地说。可李德裕已兀地转过身,三步一颠五步一踱地走了。只有吉贝被和定情线,无言地躺在地上。
秋玉傻呼呼地发愣,多情的眼睛里象熄灭了跳荡的火焰,豆大的泪珠无奈地掉到地上。秋风轻轻吹来,清早的阳光慵慵地洒来,是嘲弄,还是慰惜,秋玉不去理会,只顾钉在那里。好一会儿,她冷不防转过身去,跌跌撞撞地奔进屋里,咬紧牙关,猛地扑下身子,对着被子就要动手……
“孩子,谁欺负你啦?”幸好帕威来得正是时候,他一把夺过剪刀,关切地望着秋玉问。
“没有,没有,”秋玉背过脸,悄悄擦干了眼泪。
“没有?那你大清早为何哭了?你说,你说,谁家小子欺负了你?”帕威来了火气,磨拳擦掌,“瞧我不凑他!”
“没有,没有谁呀!”秋玉宁愿把委屈咽在肚里,也不肯惊动阿爹。
帕威哪里相信?他想起来了。路上他遇到李德裕,俩人不搭上两句三句,李德裕却匆匆走了,而且神色极为痛苦、难堪。莫非其中有什么蹊跷?
“李大人欺负了你?”帕威冷冷地问。
“不是,不是!阿爹,你千万别这样说!是女儿——”秋玉哽咽住,突然,一头扑进帕威怀里,“哇”地一声哭了,“女儿命好苦哇!”
帕威瞧着女儿这个模样,又望着地上的吉贝被和定情带,顿时明白了一切。
“孩子,李大人是好人,好人,”帕威苦笑着,“可是,这不行呀!”
“爹,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秋玉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帕威,一下子离开他的怀抱。
“孩子,你难道不明白?他是汉人,而咱,咱是黎人!”
“汉人怎样,黎人又怎样?”
“自古至今,黎汉可不不通婚呀!”帕威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要你说,不要你说!”秋玉汹汹地嚷。
“孩子,你要想想,李大人都……老啦,可是你——”
“我不要想,什么也不想!哪怕跟他过一天,我也心甘情愿!”秋玉那样子,绝不容得帕威说半个“不”字。
“唉,孩子,你也太任性了!就算依了你,也得瞧人家乐意不乐意!咱只听说挑土糊壁,不听说挑壁去糊土呀!”而对女儿的挑战,帕威也无可奈何。
“阿爹,女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你真的没有办法?”秋玉得寸进尺,使劲摇着帕威的手求援。
“好啦好啦,你就别再嚷好不?”犟父亲毕竟缠不过多情女,只好答应说,“让阿爹想想办法!”
转眼间,秋草黄了,北雁南来,划破了长空的寂寥。
李德裕不时仰望南来飞雁,喃喃自语。几天来,他草拟了几封书信和几道奏章,他想向旧时亲友一抒离情,向朝庭申辩自己的曲弯。然而,关山阻塞,投书无路,大雁也不理会他的心绪,替他捎送书信,空留一阵阵呜叫,徒增他的惆怅。
一天,帕威又上门来请李德裕。
俩人一见面,话儿可就多了。话题自然首先集中到兴修水利,开荒扩神的事情上来。帕威一拍胸脯,明年开春一定要发动峒里男女老幼,把沟渠修通南木河,连着昌化溪,把山前寨后开出一片片良田,李德裕提议把多港间道开宽、填平,方便商人进山,方便山里人到崖州做买卖。帕威一听,乐得咧开嘴笑。李德裕不慌忙地说,他要召集黎家子弟,农闲时就给他们讲学,传授中原文化.不待李德裕说完,帕威就手舞足蹈,“好,太好了!咱再认得几个字,就告一告那狗官!咱黎家人也有出头的日子过!”
“峒长,你也要告我?”李德裕哈哈地逗趣起来。
“谁是狗官,就告谁!大人,你若跟那狗官一般,咱也告你!”帕威直楞楞地说。
“峒长,别告起我来!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还得多多仰仗峒长的鹿茸来补补身子!”李德裕依然笑着。
“鹿茸,都包给大人好罗!”帕威点点头,摊开两只手掌,“不过,有一件事,还得请大人——”
“有话直说嘛!峒长向来直来直去,怎么说半句留半句起来啦?”李德裕望着帕威说。
“好,有大人这句活,咱就恳请大人了!”帕威如释重负地说,“秋玉病了,还得请大人看她一回。”
“唉,这是真的?她几时病啦?”李德裕焦急地问。
“这还有假!”帕威说得一本正经的,亟力使李德裕信以为真,“孩子都病四、五天了。”
“哟,这孩子……“李德裕叹了一口长气,脸上堆满凄楚的神色。怪不得四天五天来,他很少见到秋玉。几天前偶尔见到她时,她老远地转过身去。他明白,她还窝着气。那气里面,有恨,更有爱。人就是这样,爱到极点,就变成恨了。他不禁暗地责问自己:风烛残年,得到一颗美丽炽热的心灵的安慰,弥补创伤的灵魂裂口,这在多少人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可自己为啥要拒人于门外,自找苦吃的同时也使那颗善良的心同遭破碎?多少回,李德裕果真要回心转意了。然而,每每这个时候,他的耳畔似乎响着另一个声音:你绝不能自私,绝不能糟蹋一个美好的青春。事情会慢慢过去的。她的爱,其实是一时冲动,是一种报恩,是一种牺牲。你何必接受这种牺牲?这个时候,李德裕便忏悔起来,责备自己不该有过非分之念。况且,有一天晚上,茂光、刘松竟先后下跪,苦苦相劝他:“大人,咱们什么可都依你,这一次,你却无论如何也要听咱们的。不错,峒长好,秋玉好。可是,你是一个堂堂重臣,一时的举动,会毁了你一世英名啊!只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会嘲笑你娶了一个黎妞,胡思进更不会放过你,诬谄你勾结顽黎造反,也就有了另一条证据。大人,太可怕了!你可要听咱们这一回啊!”当时,李德裕心里烦躁,呵责两人,“尔等别捕风捉影 一派胡言! ”然而,他也明白这蛛丝马迹,自己的一举一动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他的亲人。骂归骂了,他想起他们的话来,可心有余悸。就因为这一切,李德裕强制自己把过去的都忘掉。然而,他要忘掉,别人却忘不了。李德裕好心痛呀。他料想,秋玉的病是冲着他来的。可是自己有啥办法?心病还得心药医,这心药却万万使不得。做人难,做一个堂堂正正、面面讨好的 人,就更难了!
“大人,难道咱咱请不动你?”帕威见李德裕光顾叹气,可按捺不住了。
“好,我就去!”李德裕可身不由己啊。
一路上,李德裕问起秋玉的病情,没完没了。奇怪的是,帕成似乎有意避开问话,东家长西家短地挪话来搪塞。一个粗汉也学会绕弯子,好教李德裕顿生疑团。心中生疑,越要刨根问底。帕威招架不住,反倒信口开河,半真半假地说山里有啥有啥草药,就是少了一个郎中。李德裕惊喜道, “峒长,你也认得这么多草药?以后,你教我好了,咱就用草药治病!”
说话间,秋玉的寮房到了。屋后那一丛丛刺竹,还是凤尾森森,摇曳盎盎翠色,屋旁一棚相思豆,依然叶茂枝繁,荚大籽圆。无意间,李德裕瞥见这多情物,久违了的情思悄然袭上心头,不禁贪看了几眼,才缓缓走进那间小屋。
秋玉正躺在床上,锦被盖了她的身子,单露出一张脸来。李德裕进门时,她投去一瞥,半是委屈,半是情深,便嘘了一口长气,转身向着墙壁。
“孩子,还不起来!李大人看你来了!”她母亲轻轻喊道,便要扶起秋玉。
秋玉似乎睹住气,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孩子,你不可托大!成天盼着李大人,李大人来了,你却摆起架子,也太任性了!”秋玉母亲生怕女儿惹了人家生气,用黎话责怪、催促孩子,“还不快起来!”
李德裕少不了嘘寒问暖,细细探问秋玉病情。两老口也不多说什么,只顾叹气,“咱的女儿命苦,命苦哇!”
突然,秋玉在被窝里抽泣起来。那声音起先还是时轻时重,时断时续 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催人泪下。
李德裕不由得挪近床前,百般安慰这伤心的女子。突然,秋玉掀开被子,兀地坐起,一把抹干泪水,对李德裕冷笑着,“大人,你别管我!咱是个黎妞,而你是汉人,是大官,咱哪里配得上你?咱太傻了,太傻了……”
“秋玉,别这样说嘛!”李德裕一听秋玉的愤激之词有如乱箭刺心,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白自己的心迹。
刹那间,秋玉的母亲、父亲,先后双膝跪地,对着李德裕直叩头,“大人,你可别计较孩子。她任性,直肠直肚的冲撞了大人。可她是一心一意向着你呀!她为你,都熬出病来了。大人,她的一片心,也是咱黎家的心意哪。大人,咱早把你看作自家人了,难道你对咱们还见外?你是有肝有肺的堂堂正正的好人,天塌下来也撑得起。咱若是连累了你,大人也是挑得起那千斤重担。大人,你就可怜可怜这孩子,成全了她吧!”
一切似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此刻,当一束束炽烈的、恳求的光束,久久地凝注在身上时候,当一声声深情的,披肝沥胆的呼唤扑向他的时候,他动情了,仿佛一个自甘淡泊的人,一下子得到充裕的、过分的赏予,感到手足无措,感到无言以对。但就也在这个时候,他的脑际闪过茂光、刘松的身影,耳畔响着那发自肺腑的呼告:”大人,太可怕了!你可要听咱们这一回啊!”李德裕惶惑了,迟疑着,久久才说,“峒长,容我想想吧!”
“大人,你还要想想,想到什么时候?这孩子都愁煞人了,可你……”秋玉母亲声泪皆下,“大人,你真的这样心?”
“是呀,大人,你难道真地这么狠心?”帕威眼巴巴望着李德裕。
“狠心?是呀,峒长,我竟这么狠心,成了个无仁无义之人!”李德裕有口难辩,冷笑不止,“我好狠心,好狠心呀!”
突然,秋玉一骨碌滚起,从藤箩里出掏来那张簇新的锦被和那条定情线,一古脑儿摔在地上,然后,双腿跪在被上,对着帕威两老施了大礼,“阿爹,阿妈,不要为难李大了。咱命薄,没有福气,女儿认命了。阿爹,阿妈,你们的大恩大德,女儿几辈子也报答不了,来生再作牛作马,报答阿爹阿妈的大恩大德!”秋玉说着说着,早已泪如雨下。帕威赶忙扶起她,可秋玉执意不起。她又转身对着李德裕行了大礼,“大人,你待咱好,咱谁也不怪,只怪自己!你要多多保重!”秋玉说完,猛地拿起剪刀,把锋利的刀尖对准喉咙,“咱该去了,留一条贱命有何用处?”
帕威吓坏了,抢过剪刀,搂住女儿,放声哭了。
李德裕一时呆呆痴痴,想不到一个温柔的女子竟然这么痴情,这么刚烈,刹那间,什么顾虑,什么犹豫,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望着秋玉,淌出了泪花,忘情地自言自语,“秋玉,你你情深义重,我……”
“大人,你就成全了小女吧!”帕威同老伴再一次下跪,“这是秋玉的心意,也是咱多港峒男女老少的心意!咱黎胞和汉族同胞,为啥不是一家人呢?”
“峒长,请起,请起!”李德裕躬身扶起两人,“我什么时候说不行呀?今天,我就首先拜谢峒长了!”
大家笑了,开心地笑了。那盈盈的笑,比雨后的彩霞还要美了几分。
远处,那一片苍黑的林子里,荔枝树上挂满一串串酡红的荔枝果;近处,翠绿的山坡上,山柚果熟了,桃金娘熟了,野芭蕉熟了,绿丛间点缀着嫣紫嫩黄。松鼠们、野鸡们窜来窜去,上飞下跳,忙碌地消受着秋天的馈赠。
抱班寨里头次种下水稻,就获得好收成。村头寨尾人们相遇了,便要停下来嘀咕一番。明知道对方家里稻谷成堆,偏要问今年收成不赖吧;明明是心里乐开了花,却发愁说缺了个大谷围。这个说天开了眼,那个说帅公来得好,于是一齐眉开眼笑,忙坏了腰。
夕阳快下山了,秋玉还在场上槌着谷子。她槌着槌着,却忍不住放下木棒,撮一撮黄澄澄的谷子放在掌心里,捻来捏去,啧啧地赞不绝口,“多好的谷子!阿爹,你来看看!”
“傻孩子,你说过几遍了?阿爹看了十次八次罗!”帕威笑嘻嘻的,“乖孩子,谷子都填进腹里,饱啦?还不快吃饭!”
“阿爹,你儿时请李大人来尝新?人家不来,谷子该不会从天上飞下来吧!”秋王咂咂嘴。
“那当然,当然,要请李大人尝新!”帕威点点头,突然叹了叹气,“咱只怕——”
“怕什么?”秋玉吃了一惊。
“只怕明年李大人……他他要回京城罗!”帕威瞧女儿那副模样,第一次撒起谎来。
“不会的,不会的!阿爹,你胡说……李大人的家不是在在这……”秋玉一听失了神,傻乎乎的,脸也刹时惨白。
帕威可吓坏了。他连忙扶起秋玉,一遍一遍咒骂自己,象哄小孩似的哄着秋玉,“傻孩子,李大人真要走,咱也会拉住他!李大人早说过,真让他回去当皇帝,他也不走了!”这后一句,其实是帕威给女儿定心丸吃,故意编出来的。
秋玉这才破涕为笑。她收工吃过晚饭,又忐忑不安起来,勿勿回到寮房。
月亮升起了。
蓝天里悬着一面玉镜,屋前一汪清水潭里也闪动一面玉镜。多少个花月夜,秋玉曾对着它,照一照姣好的脸蛋,阿光也曾对着它,照一照英武的身影,然后,才双双走向蓝幽幽的小路。那时,月光是粉,匀匀地筛下来,往她脸上撒上薄粉,着上淡装,把她打扮成一个玉女。那时,月光是水,把层峦叠嶂洗得象一堆堆翡翠,把半腹子愁烦洗净,只剩下柔肠七尺,七尺柔肠。后来,阿光撇下她走了。她也曾想跟阿光一道去了,后来则想这辈子孤单一人活下去。不管怎么说,这一汪水潭近在咫尺,她从那时起就躲着它,白天夜里都躲着它。然而,今晚秋玉躺在床上,却无法宁静思绪。她身不由己,走出房外,走到清水潭边,依然倚靠在那株菠萝蜜树上……
一会儿,传来了唎咧的声音,那跳荡着欢乐,跳荡着激情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秋玉突然转过身,走回寮房,蒙起被子躺下,一头嘟哝着,“烦死人了!”
这时,多情的歌儿飞进寮房:
想死你呀好妹妹,
想到石头上开花,
想到马儿长出角,
想到树皮不生麻……
真想灌你迷魂药呀,
我的好妹妹!
秋玉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她分不清是无奈还是应酬,是绝望还是企盼,到底是掀开被子,在床上翻过身,叹了叹气,这才一骨碌爬起。
几个英俊的小伙子走到门口外边。人未进门,歌儿先闯进门口:
妹妹的寮宽房又宽,
妹妹的竹床凉又凉。
哥想坐到侬身边,
只求妹妹把口张。
秋玉款款起身,搬过板凳,排上几口槟榔,请客人尝尝,请客人赏光,然后,慢慢唱了起来:
哥哥有心来相伴,
妹妹有心也枉闲。
屋前花株已有主,
一花难得两家栽。
此处不卖别处买,
东市无鱼走西海。
有志打石石都开,
何愁不得好花栽。
秋玉委婉地把向她求爱的小伙子打发走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夜、两夜的事情。然而,人走了,那悠悠的口弓声、鼻箫声,似乎还回荡在屋子里面。此刻,那声音就是蜿蜒的青溪,而她一颗心就是青溪底部晶莹的卵石,任着流水冲刷,冲出了怅惘,冲出了苦涩,冲出了焦灼的渴望。秋玉兀自苦笑着,咱这株花有主,那末,主是谁呢?咱为啥要对人家说谎呢?她痛苦地闭上眼睛,朦胧中分明有谁走来,那样面熟,却又那样陌生。对了,他是咱的“主”,快挽住他,别让他跑掉。秋玉不觉叫出声来,睁开眼睛,床上人单影独,屋外也只有清冷的月影。她觉得无边的失落,倚在门上怅然而望。她多么想见到那桔黄色的灯光见到那梦中常常出现的身影!然而,那灯光,那身影,都被一间间船形屋挡住了。人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越发使秋玉惆怅不已。
又是一个明媚的秋日。
太阳刚爬过对面山头,帕威就请来了李德裕。他最近腌制的鹿肉茶刚开缸,自然要请李德裕品尝一番。
“大人,你慢慢地吃,慢慢喝,看咱的茶,酒蜜,比皇帝给你吃的、喝的怎么样?”帕威大献殷勤,带着二十分的期待说。
李德裕果真慢吃慢喝,不时咂一咂嘴唇,不时看一看帕威那个得意劲儿。他已明白帕威期待的是什么,却摇了摇头说,“比皇宫里吃的、喝的,差多了!”
“什么?”帕威突然沉下脸来,“咱黎家的,怎差?你不说个明白,今后咱不再请你!”
“真的?”李德裕嘿嘿笑着问。其实,李德裕逗逗他罢了。刚刚尝上茶,李德裕觉得有点腻,等到茶入肠胃,才觉得有一股清甜淡香的气味沁上喉咙,全身瞬间变得无比爽快,比宫庭佳肴胜了五分。那酒蜜更是妙不可言:起先,一丝清甜、几许香馥,透过喉咙,进入肺腑,渗入每个孔窍。以后,那香、那甜,变成发酵剂,把片刻领略到的无比快慰,酿造成韵味无穷的享受。当下,帕威生气,倒逗得他直乐。他连忙改过口来,“峒长,皇宫里的,比咱的差多了,差多了!你刚才不听明白。改日我还要给茶和酒蜜写写文章,传播出去,留给后人!”
帕威转怒为喜,一个劲儿给李德裕灌起酒来。
秋玉在一旁可急坏了。她知道李德裕酒量不大,万一喝多了,身子消受不了,就麻烦了。她几次抢过少埕子,不让帕威倒酒,可是帕威哪里肯依?此刻,他的千般情,万般意,全在酒中了。
秋玉不想让父亲扫兴,又不想让李德裕坏了身子,一时无计可施,急红了脸。幸好她脑子灵,乘着帕威不在意,捧上一碗鹧鸪茶,来了个偷梁换柱,悄悄端起李德裕面前那碗酒,“阿爹,孩子陪你们喝!”说完,她一饮而尽,才深情地对着李德裕,“李大人,该你喝了!”
李德裕一时还愣住,禁不得秋玉再三恳请,才慢慢呷了起来。才呷几口,他便觉得味道不同,热烘烘的脑门也清爽几分。他好生奇怪,直到悟出秋玉以茶代酒帮了他的忙,才叹息着,“多亏这孩子有心!”
几天过去了。秋玉织好了一张闪亮簇新的黎锦,却直盯住上面的花花草草出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想让他爹拿给李德裕,她又想亲自给他送去。可她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好办法,最后,鼓起勇气去请李德裕。
秋玉有满腹话要说,却觉得无从说起,一路走来,心里都象给猫抓一样。向阳坡上,一对班鸠扑腾扑腾着,从低枝跳上了高枝。顿时,她脸颊抹上灿灿秋光,一对乌亮的眸子闪着兴奋的光芒,连那说话的声音也格外动听,“大人,斑鸠鸟咕咕喊,它们喊的是啥呀?”
李德裕摇了摇头,饶有兴致地问,“阿玉,你就能听得出鸟的说话?”
“怎么不?”秋玉咂了咂嘴巴。
“哟,那你就说给我听听!”李德裕笑了笑。
“大人,你猜一猜罗!那只雌鸟跟着雄鸟,一步不离,它们会说什么? ”秋玉调皮地扮了一个怪相。
“它们说今天你好高兴呀!”李德裕有意逗一逗秋玉。
“大人,你又编派人了!雌的骂雄鸟……傻……”秋玉涨红了脸,不再说下去。
他们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地,秋玉的寮房出在眼前。突然,李德裕一下子敛声敛气的,刹地停住脚步。
“大人,你嫌咱这屋子小吧?”秋玉逗笑着,哪里晓得李德裕的心事!这是他同夫人生离死别之地。如今风景依旧,人事已非,当然会勾起李德裕满腔悲愤。而且,李德裕也知道,这小小草屋,是黎家子女耕耘着爱情的一块热土。它只能属于年轻一代,而他,早已是爱情青树上的一张秋后黄叶。面前那低矮的门槛,早已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台阶。当然,这一切秋玉並不是毫无所知,但多少天来,她望着李德裕孤身一人,撑住生命的小舟,她于心不忍呀,出于感激、敬仰,出于同情、怜悯,她铁定决心,想去填补李夫人空下来的位置。她认为唯有这样做,才能给李德裕最大的温暖,给她自己无边的快慰。至于面前的深谷沟壑,她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甚至根本不愿去想。这些日子,一个心底的呼唤,使她把少女的自尊都豁了出去。就是面前有火海,有刀山 她也决不犹豫、彷徨,毫无反悔地朝前走。今天,她请 李德裕前来看看黎锦,为的是好好乘机表白心迹。此刻,她可谓情迷心窍,也就不理会李德裕的心事了。
“不小……不小……”李德裕吱唔着,神态异常尴尬呆在那里不动。
秋玉慌里慌张,匆忙跑进屋里抱出来一张吉贝被,“大人,冬天快来啦。这被子,你就拿去遮遮寒吧!”
“秋玉,你的情我领了。这被子,你还是留住日后用吧!”李德裕难为情地推辞着。
“大人,你不要被子,你……你……你瞧不起咱!”秋玉噘起嘴巴,汹声汹气地说。
李德裕一愣,不由双手接过吉贝被来。一打开,双手却不停地哆嗦;他捧不住苍山碧海,捧不住顶天的石柱,捧不住成双成对的五色雀,捧不住被里包着的一条定情带!他脸色发白,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大人,你,你怎么啦?”秋玉赶忙扶住李德裕。
“我……,我……我患了风寒……会好……”李德裕结结巴巴地说。
“大人,进屋里歇息吧!咱煮药给你喝,煮热粥喂你,咱什么都愿意为你做!”秋玉喋喋不休地说。可李德裕已兀地转过身,三步一颠五步一踱地走了。只有吉贝被和定情线,无言地躺在地上。
秋玉傻呼呼地发愣,多情的眼睛里象熄灭了跳荡的火焰,豆大的泪珠无奈地掉到地上。秋风轻轻吹来,清早的阳光慵慵地洒来,是嘲弄,还是慰惜,秋玉不去理会,只顾钉在那里。好一会儿,她冷不防转过身去,跌跌撞撞地奔进屋里,咬紧牙关,猛地扑下身子,对着被子就要动手……
“孩子,谁欺负你啦?”幸好帕威来得正是时候,他一把夺过剪刀,关切地望着秋玉问。
“没有,没有,”秋玉背过脸,悄悄擦干了眼泪。
“没有?那你大清早为何哭了?你说,你说,谁家小子欺负了你?”帕威来了火气,磨拳擦掌,“瞧我不凑他!”
“没有,没有谁呀!”秋玉宁愿把委屈咽在肚里,也不肯惊动阿爹。
帕威哪里相信?他想起来了。路上他遇到李德裕,俩人不搭上两句三句,李德裕却匆匆走了,而且神色极为痛苦、难堪。莫非其中有什么蹊跷?
“李大人欺负了你?”帕威冷冷地问。
“不是,不是!阿爹,你千万别这样说!是女儿——”秋玉哽咽住,突然,一头扑进帕威怀里,“哇”地一声哭了,“女儿命好苦哇!”
帕威瞧着女儿这个模样,又望着地上的吉贝被和定情带,顿时明白了一切。
“孩子,李大人是好人,好人,”帕威苦笑着,“可是,这不行呀!”
“爹,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秋玉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帕威,一下子离开他的怀抱。
“孩子,你难道不明白?他是汉人,而咱,咱是黎人!”
“汉人怎样,黎人又怎样?”
“自古至今,黎汉可不不通婚呀!”帕威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要你说,不要你说!”秋玉汹汹地嚷。
“孩子,你要想想,李大人都……老啦,可是你——”
“我不要想,什么也不想!哪怕跟他过一天,我也心甘情愿!”秋玉那样子,绝不容得帕威说半个“不”字。
“唉,孩子,你也太任性了!就算依了你,也得瞧人家乐意不乐意!咱只听说挑土糊壁,不听说挑壁去糊土呀!”而对女儿的挑战,帕威也无可奈何。
“阿爹,女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你真的没有办法?”秋玉得寸进尺,使劲摇着帕威的手求援。
“好啦好啦,你就别再嚷好不?”犟父亲毕竟缠不过多情女,只好答应说,“让阿爹想想办法!”
转眼间,秋草黄了,北雁南来,划破了长空的寂寥。
李德裕不时仰望南来飞雁,喃喃自语。几天来,他草拟了几封书信和几道奏章,他想向旧时亲友一抒离情,向朝庭申辩自己的曲弯。然而,关山阻塞,投书无路,大雁也不理会他的心绪,替他捎送书信,空留一阵阵呜叫,徒增他的惆怅。
一天,帕威又上门来请李德裕。
俩人一见面,话儿可就多了。话题自然首先集中到兴修水利,开荒扩神的事情上来。帕威一拍胸脯,明年开春一定要发动峒里男女老幼,把沟渠修通南木河,连着昌化溪,把山前寨后开出一片片良田,李德裕提议把多港间道开宽、填平,方便商人进山,方便山里人到崖州做买卖。帕威一听,乐得咧开嘴笑。李德裕不慌忙地说,他要召集黎家子弟,农闲时就给他们讲学,传授中原文化.不待李德裕说完,帕威就手舞足蹈,“好,太好了!咱再认得几个字,就告一告那狗官!咱黎家人也有出头的日子过!”
“峒长,你也要告我?”李德裕哈哈地逗趣起来。
“谁是狗官,就告谁!大人,你若跟那狗官一般,咱也告你!”帕威直楞楞地说。
“峒长,别告起我来!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还得多多仰仗峒长的鹿茸来补补身子!”李德裕依然笑着。
“鹿茸,都包给大人好罗!”帕威点点头,摊开两只手掌,“不过,有一件事,还得请大人——”
“有话直说嘛!峒长向来直来直去,怎么说半句留半句起来啦?”李德裕望着帕威说。
“好,有大人这句活,咱就恳请大人了!”帕威如释重负地说,“秋玉病了,还得请大人看她一回。”
“唉,这是真的?她几时病啦?”李德裕焦急地问。
“这还有假!”帕威说得一本正经的,亟力使李德裕信以为真,“孩子都病四、五天了。”
“哟,这孩子……“李德裕叹了一口长气,脸上堆满凄楚的神色。怪不得四天五天来,他很少见到秋玉。几天前偶尔见到她时,她老远地转过身去。他明白,她还窝着气。那气里面,有恨,更有爱。人就是这样,爱到极点,就变成恨了。他不禁暗地责问自己:风烛残年,得到一颗美丽炽热的心灵的安慰,弥补创伤的灵魂裂口,这在多少人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可自己为啥要拒人于门外,自找苦吃的同时也使那颗善良的心同遭破碎?多少回,李德裕果真要回心转意了。然而,每每这个时候,他的耳畔似乎响着另一个声音:你绝不能自私,绝不能糟蹋一个美好的青春。事情会慢慢过去的。她的爱,其实是一时冲动,是一种报恩,是一种牺牲。你何必接受这种牺牲?这个时候,李德裕便忏悔起来,责备自己不该有过非分之念。况且,有一天晚上,茂光、刘松竟先后下跪,苦苦相劝他:“大人,咱们什么可都依你,这一次,你却无论如何也要听咱们的。不错,峒长好,秋玉好。可是,你是一个堂堂重臣,一时的举动,会毁了你一世英名啊!只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会嘲笑你娶了一个黎妞,胡思进更不会放过你,诬谄你勾结顽黎造反,也就有了另一条证据。大人,太可怕了!你可要听咱们这一回啊!”当时,李德裕心里烦躁,呵责两人,“尔等别捕风捉影 一派胡言! ”然而,他也明白这蛛丝马迹,自己的一举一动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他的亲人。骂归骂了,他想起他们的话来,可心有余悸。就因为这一切,李德裕强制自己把过去的都忘掉。然而,他要忘掉,别人却忘不了。李德裕好心痛呀。他料想,秋玉的病是冲着他来的。可是自己有啥办法?心病还得心药医,这心药却万万使不得。做人难,做一个堂堂正正、面面讨好的 人,就更难了!
“大人,难道咱咱请不动你?”帕威见李德裕光顾叹气,可按捺不住了。
“好,我就去!”李德裕可身不由己啊。
一路上,李德裕问起秋玉的病情,没完没了。奇怪的是,帕成似乎有意避开问话,东家长西家短地挪话来搪塞。一个粗汉也学会绕弯子,好教李德裕顿生疑团。心中生疑,越要刨根问底。帕威招架不住,反倒信口开河,半真半假地说山里有啥有啥草药,就是少了一个郎中。李德裕惊喜道, “峒长,你也认得这么多草药?以后,你教我好了,咱就用草药治病!”
说话间,秋玉的寮房到了。屋后那一丛丛刺竹,还是凤尾森森,摇曳盎盎翠色,屋旁一棚相思豆,依然叶茂枝繁,荚大籽圆。无意间,李德裕瞥见这多情物,久违了的情思悄然袭上心头,不禁贪看了几眼,才缓缓走进那间小屋。
秋玉正躺在床上,锦被盖了她的身子,单露出一张脸来。李德裕进门时,她投去一瞥,半是委屈,半是情深,便嘘了一口长气,转身向着墙壁。
“孩子,还不起来!李大人看你来了!”她母亲轻轻喊道,便要扶起秋玉。
秋玉似乎睹住气,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孩子,你不可托大!成天盼着李大人,李大人来了,你却摆起架子,也太任性了!”秋玉母亲生怕女儿惹了人家生气,用黎话责怪、催促孩子,“还不快起来!”
李德裕少不了嘘寒问暖,细细探问秋玉病情。两老口也不多说什么,只顾叹气,“咱的女儿命苦,命苦哇!”
突然,秋玉在被窝里抽泣起来。那声音起先还是时轻时重,时断时续 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催人泪下。
李德裕不由得挪近床前,百般安慰这伤心的女子。突然,秋玉掀开被子,兀地坐起,一把抹干泪水,对李德裕冷笑着,“大人,你别管我!咱是个黎妞,而你是汉人,是大官,咱哪里配得上你?咱太傻了,太傻了……”
“秋玉,别这样说嘛!”李德裕一听秋玉的愤激之词有如乱箭刺心,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白自己的心迹。
刹那间,秋玉的母亲、父亲,先后双膝跪地,对着李德裕直叩头,“大人,你可别计较孩子。她任性,直肠直肚的冲撞了大人。可她是一心一意向着你呀!她为你,都熬出病来了。大人,她的一片心,也是咱黎家的心意哪。大人,咱早把你看作自家人了,难道你对咱们还见外?你是有肝有肺的堂堂正正的好人,天塌下来也撑得起。咱若是连累了你,大人也是挑得起那千斤重担。大人,你就可怜可怜这孩子,成全了她吧!”
一切似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此刻,当一束束炽烈的、恳求的光束,久久地凝注在身上时候,当一声声深情的,披肝沥胆的呼唤扑向他的时候,他动情了,仿佛一个自甘淡泊的人,一下子得到充裕的、过分的赏予,感到手足无措,感到无言以对。但就也在这个时候,他的脑际闪过茂光、刘松的身影,耳畔响着那发自肺腑的呼告:”大人,太可怕了!你可要听咱们这一回啊!”李德裕惶惑了,迟疑着,久久才说,“峒长,容我想想吧!”
“大人,你还要想想,想到什么时候?这孩子都愁煞人了,可你……”秋玉母亲声泪皆下,“大人,你真的这样心?”
“是呀,大人,你难道真地这么狠心?”帕威眼巴巴望着李德裕。
“狠心?是呀,峒长,我竟这么狠心,成了个无仁无义之人!”李德裕有口难辩,冷笑不止,“我好狠心,好狠心呀!”
突然,秋玉一骨碌滚起,从藤箩里出掏来那张簇新的锦被和那条定情线,一古脑儿摔在地上,然后,双腿跪在被上,对着帕威两老施了大礼,“阿爹,阿妈,不要为难李大了。咱命薄,没有福气,女儿认命了。阿爹,阿妈,你们的大恩大德,女儿几辈子也报答不了,来生再作牛作马,报答阿爹阿妈的大恩大德!”秋玉说着说着,早已泪如雨下。帕威赶忙扶起她,可秋玉执意不起。她又转身对着李德裕行了大礼,“大人,你待咱好,咱谁也不怪,只怪自己!你要多多保重!”秋玉说完,猛地拿起剪刀,把锋利的刀尖对准喉咙,“咱该去了,留一条贱命有何用处?”
帕威吓坏了,抢过剪刀,搂住女儿,放声哭了。
李德裕一时呆呆痴痴,想不到一个温柔的女子竟然这么痴情,这么刚烈,刹那间,什么顾虑,什么犹豫,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望着秋玉,淌出了泪花,忘情地自言自语,“秋玉,你你情深义重,我……”
“大人,你就成全了小女吧!”帕威同老伴再一次下跪,“这是秋玉的心意,也是咱多港峒男女老少的心意!咱黎胞和汉族同胞,为啥不是一家人呢?”
“峒长,请起,请起!”李德裕躬身扶起两人,“我什么时候说不行呀?今天,我就首先拜谢峒长了!”
大家笑了,开心地笑了。那盈盈的笑,比雨后的彩霞还要美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