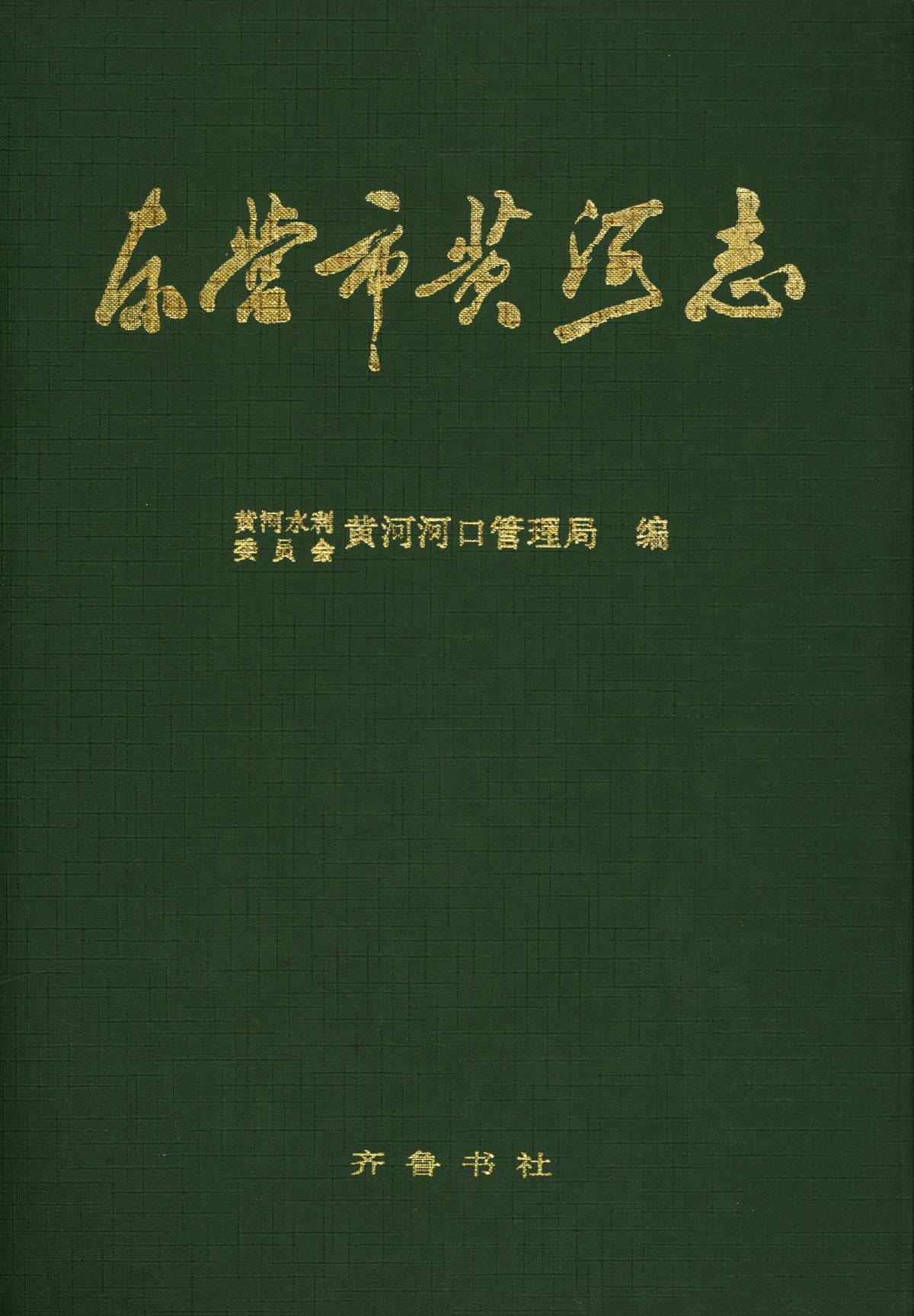内容
第一节流路变迁
一、变迁过程黄河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以来,因人为或自然因素在宁海为顶点的三角洲扇面上决口、分汊、改道频繁。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调查统计,决口改道达50余次,其中导致尾闾流路变迁9次(参见图4—1)。各条流路行水情况如下:
(一)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铜瓦厢三堡(今东坝头)决口。溃水至山东东阿张秋镇穿运河入大清河河道后,流经平阴、东阿、齐河、济南、济阳、齐东、惠民、高苑、蒲台、滨州等地至利津县沿宁海、十六户、薄家庄、台子庄、韩家垣在铁门关以北、肖神庙以下之二河盖牡蛎嘴入海。历时34年,实际行水19年(其余时间系因上游傍决改道而干河,下同)①。
(二)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韩家垣漫溢决口,溃水在老鸹岭附近分汊后,又在付家窝附近合股归一,经四段及杨家嘴至毛丝坨以下(今建林东)入海。山东巡抚张曜以其地距海较近而不堵塞决口,在两岸各筑新堤三十里束水中行,历时8年,实际行水5年又10个月。
图4一1黄河河口流路变迁图
(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北岭、西滩两地漫决。不久,西滩口门渐被淤塞,大溜全注北岭,溃水由薄家庄南东流,过集贤村转向东南,经左家庄、永安镇、老十五村由丝网口(今宋家坨子)以下团坨子以北入海;另有支汊一股在乱井子(清河村旧址)西北分流,又在羊栏子与三十八户之间合一,历时7年,实际行水5年又9个月。
(四)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薄家庄决口,河经青边岭、虎滩嘴、流口、薄家屋子、义和庄入徒骇河下游绛河故道,在太平镇以北老鸹嘴入海。13年后此道淤塞,又在太平镇改行东北经大洋铺、中和堂在车子沟入海;另由虎滩嘴东南、陈家屋子北分出岔河,经大牟里、小牟里、四扣在刘家坨子、韩家屋子以北面条沟(今挑河)入海。民国14年(1925年)又在虎滩嘴分岔向西北岀沾化入无棣由套尔河入海。此次北流入海历时22年,实际行水17年又9个月 (按:有的文献曾以太平镇改道前后作为两次变迁记载)。
(五)民国15年(1926年)6月,八里庄以北(吕家洼)决口,向东北经丰国镇(今汀河)沿铁门关故道及沙子头(刁口河)入海,历时3年。
(六)民国18年(1929年)8月,纪家庄盗掘大堤成口东泄,河经义和村、东张、西双河、民丰、一村等地,初由南旺河(今支脉沟)入海,7、8个月后又在乱井子以南改行东南,至民丰以北入第3次行水故道;一年后又在永安镇以南改向,经下镇由宋春荣沟入海;行水两年后,复在永安镇西南改向青坨子入海。历时5年,实际行水3年又4个月。
(七)民国23年(1934年)8月,合龙处(今涯东村)决口,溃水向东漫流,先由毛丝坨以北老神仙沟入海;后又形成神仙沟、甜水沟、宋春荣沟三路入海形势。民国27年(193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军队在郑州花园口掘堤,黄河改由徐淮故道注入黄海,山东河竭。民国36年(1947年)3月,花园口口门堵复,黄河重归山东仍循甜水沟(过水约七成)、神仙沟(过水约二成)、宋春荣沟(过水近一成)分注渤海。历时19年,实际行水9年又2个月。
(八)黄河归故后的三条入海路线以甜水沟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沟淤积延伸,行程加长,比降变小(平均万分之一),河形蜿蜒曲折。相对神仙沟行程较短,比降较大,过水比例逐渐增加,并在小口子村附近形成两河弯顶相向发育,至1953年两弯顶相距仅95米,有自然沟通之势。遂因势利导于当年7月在两弯顶之间开挖引河,促成神仙沟独流入海。历时10年又5个月。
(九)1964年凌汛,罗家屋子以下河道卡冰壅水漫滩,危及河口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查勘研究,山东省委授权由惠民地委决定,于1964年1月1日在罗家屋子爆破民坝分泄凌洪,由草桥沟、洼拉沟入刁口河漫流归海。5月,新流路过水六成以上,终成改道刁口河。行水12年又5个月。
(十)1976年5月,经多年筹备改道清水沟计划付诸实施,在罗家屋子进行人工截流成功,炸开西河口引河挡水坝,改由清水沟入海。迄今已逾12年,仍在继续行水。
二、现行流路演变
清水沟是神仙沟与甜水沟之间的洼地,长27公里,地面高程较两侧地势低1.5-4.0米,入海口位于两故道沙嘴间的凹湾处。
(一)河势变化(见图4-2):清水沟开始行河时水流沿引河下泄、顺自然地势向东入海,河面宽2〜3公里,主流位置居中偏南,河势散乱。清4断面以上四股水流显见,但主流过水部位偏重在南防洪堤附近,引起十八公里堤身靠溜成险。1978年春抢修护林挑水坝,截堵南部三股水道,十八公里险工溜势上提变缓,水流并为一股。清4断面以下经历四个阶段,即:1976〜1980年为淤滩造床阶段,最初漫流入海,尔后河势游荡,不断产生汊河,主溜变化不定,入海口门摆动频繁,最大摆动距离达23公里(参见表4-1),沙嘴延伸迅速;1980-1985年,河势渐趋稳定,主槽成单一状态,滩槽高差由0.74米增加至2.35米;1985〜1987年,河道淤积,清7断面以下尤重,拦门沙明显,顺河长4〜5公里,垂直河宽7公里,入海口门不畅;1988年起,为稳定现行流路,改善河口地区防洪(凌)的不利形势,实施调整入海口门,清理河道阻水障碍,修筑导流堤,在尾闾河段进行机船疏浚拖淤和截支强干,同时在西河口至十八公里间修建控导工程,对稳定河势、通畅河门起到一定作用。西河口以下出现单一顺直河槽,10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一般滩唇出水高0.5米左右。清8断面上下河槽宽800米左右,无分汊支沟,低潮时拦门沙水深仍达1.3米左右。
(二)河道冲淤:改道当年水量偏丰,沙量偏枯,利津站最大洪峰8020立方米每秒历时5天,平均含沙量仅12公斤/立方米。艾山以下河道普遍发生沿程冲刷。因改道引起的溯源冲刷也较显著。其后,河口不断淤积延伸,河长有所增加,但因河势发展较好,利津至西河口河道主槽仍保持冲刷(参见表4—2)。西河口以下虽以淤积为主,却在淤滩造床中形成单一主槽。据1987年汛前实测,利津以下河道总长为104公里,比刁口河流路末期河长尚短7公里。利津至西河口河段河床平均高程低于改道前0.31-1.08米;与改道前的3000立方米每秒同流量水位相比,西河口站低0.54米,一号坝站低0.56米,利津站低0.51米。西河口以下河道主槽高程与改道前相比,清1至清2断
黄河清水沟流路河势变迁图图4-2
清水沟流路河口延伸摆动表 表4-1
注:①1976年6〜10月延伸长度11公里;1976年10月〜1978年10月延伸长度5公里。
②“一”为蚀退。
清水沟河道主槽冲淤变化表 表4—2
注:正数为淤积,负数为冲刷。
面低1.0-0.6米,清3至清7断面淤高1.1-1.4米。滩地平均淤高:清1断面1-1米,清2至清6断面2.23-2.73米,清7断面达4.3米。
随着流路冲淤塑造发展,河床纵剖面形态亦相应的自动调整。1986年汛前利津至西河口比降约0.8‰,西河口至清7断面约1.1‰,改道点以下河床仍陡于改道点以上,但差值很小。在来水来沙的作用下,河床横剖面形态亦向窄深方向发展。西河口以下河道过水断面的变化是:清10断面以上主槽宽度由大变小,1976年主槽宽度1206-2980米,1986年缩窄到1000米左右;平槽流量下的断面平均水深由小增大,1976年0.84〜1.92米,1986年后达到1.97〜3.32米。
(三)河口淤积:改道清水沟流路初期入海位置多变,在较大范围内促使岸线普遍外延。1980年后,河道归顺单一,无大出汊摆动,沙嘴呈单一集中形式淤进,宽度在20〜30公里之间,2〜12米水深区的淤积量占观测范围内总淤积量的81%(浅海淤积总宽度为53公里)。1984年实测,浅海水下岸坡形态 (又称水下三角洲)大体分为:0〜2米等深线之间的顶坡段,比降4〜9‰;2〜12米等深线之间的前坡段,比降30〜35‰;12米等深线以下的尾坡段,比降2〜3‰。据统计,采用一2米高程线作为造陆面积的界限时;清水沟行河的1976〜1985年间,河口造陆面积累计为406平方公里,年均43.5平方公里①,入海1亿吨泥沙,平均造陆7.15平方公里。输送至河口地区的泥沙,淤积在河道和12米等深线以内海区的约占利津站输沙总量的80%左右;输至12米等深线以外的约占20%左右。近几年水文测验资料,河口沙嘴突出后,最大潮流速达2米/秒左右,比莱洲湾原潮流速值0.6米/秒显著增大;潮流速方向为涨潮向南,落潮向北,与河口射流方向大体垂直,有利于泥沙向河口两侧的输送。
三、变迁规律
50年代,黄委会水科所及河口水文站等单位开始对1855年以来近口流路变迁进行调查考证。其后,随着资料不断积累和认识逐步加深,特别对神仙沟、刁口河、清水沟3条流路的原型观测成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后,认为河口流路变迁基本遵循以下几点规律:
(一)淤积延伸摆动改道是黄河口自然演变的基本形式。每年3〜7亿吨泥沙在河口堆积后,相应改变河流侵蚀基准面高程,导致河床比降变缓,水位升高。达到一定程度后,近口流路势必自寻最小阻力捷径入海,孕育一次尾闾改道。在水沙条件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条流路的自然演变周期大体为10年左右。
(二)每条流路行水期间,平面河型演变过程为:改道初期游荡散乱→归股→单一→弯曲→出汊摆动→出汊点上移→再改道散乱。以上发育过程完成后,构成一次“小循环”。几次不同入海流路的“小循环”在三角洲洲面上从中部开始,先南后北横扫一遍后,构成一次“大循环”,三角洲岸线则普遍向海推进一次,导致河口水位进一步上升。
(三)每次尾闾变迁对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都产生直接影响。一般表现为初期流程缩短,比降变陡,改道点以上发生溯源冲刷,上界可抵刘家园或泺口,距改道点200公里左右。维持几年的低水位状态后,又开始溯源堆积或沿程堆积,河床高程平行上升,同流量水位再度升高,成为下一次流路变迁的前兆(参见表4—3) 。
(四)尾闾流路变迁可以暂缓河口地区防洪防凌压力。河口地区地势低平坦荡,防洪设施简陋,伏汛、凌汛涨水漫滩出险较多,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很大,防洪防凌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河口流路发生变迁后,河道边界条件有所改善,口门较为通畅,泄洪(凌)排沙能力增大,一般可以维持几年的低水位状态,减少洪、凌漫滩机遇,缓解防洪防凌压力。如1953年神仙沟独流入海后,不仅战胜1954年出现的7220立方米每秒、1957年岀现的8500立方米每秒等较大洪水,而且战胜了1958年岀现的10400立方米每秒大洪水。1964年元月改道刁口河以后,不几天便缓解了当时的凌汛危机。1975年汛期最大洪水仅6500立方米每秒,且有渔户村分洪口门过水,西河口水位仍然接近10米,河口地区防洪处处吃紧。但在1976年实施改道清水沟计划以后,河口地区同流量水位大幅度下落,当年岀现8020立方米每秒洪水也安然渡过。因此,在河口水沙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合理安排入海流路,实行有计划的人工干预,是解决河口摆动改道与工农业生产矛盾、减轻重大洪(凌)灾损失的有效措施(参见表4—4)。
河口变化对下游河道影响的幅度、范围及历时表 表4-3
人工干预河口改道情况表 表4-4
第二节海岸线
一、1855年前海岸线形成
黄河三角洲在古地质构造上是河淮凹陷平原的一部分。中新世中期,平原整体下陷,与当时的胶辽古陆解体,利津一带处在渤海凹陷中心的南沿。第四纪(大约200万年前开始)以来,自孟津脱谷而出的黄河及源自太行、燕山之麓的海河水系携带大量泥沙南北交替淤积,逐渐填充了长期以来的地壳下沉而成陆,沉积物厚达500-800米。大约四千年前,冲积扇延伸到泺口以东。至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年前后),利津城西、城南已成陆地凸入海中①,是西周至西汉时期先后称名齐地、千乘郡、蓼城县、湿沃县的地方。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今濮阳境)决口改道,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时,自荥阳筑堤千里,导河由千乘入海后,以利津城附近为起点向东、向北展开造陆。西汉至南北朝期间城西地区变化不大。隋至唐末(公元581-907年)的三百多年间,利津一带海岸线外延约30余里,今王庄、盐窝、北岭、董集、坨庄等处均成陆地。至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城东增至60余里。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城北又增至60余里,海岸线推进到铁门关(今前关村)一带,虎滩、汀河、陈庄、集贤、民丰等地退海成陆②。
金明昌五年(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今中牟、延津一带),形成南北分流,南河夺泗入淮,北河夺大清河(又称北清河)至利津一带入海,继续造陆。至明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主修太行堤遏制北流,全黄入淮归注黄海为止,历时300余年,海岸线又推进30余里至老爷庙一带。太平、义和、六合、付窝、西宋、永安等地相继脱海。此后,黄河之水客串利津仅属偶见,造陆剧缓,最终形成现黄河口海岸线。对此古海岸线位置的确定:一是黄委会前左河口水文实验站根据实地调查海堡分布及有关历史文献,参考航测照片判读确认的大体走向是由徒骇河(即套尔河)起,经耿家局子、老鸹嘴、大洋铺、北混水旺、老爷庙、罗家屋子、友林等地附近,至南旺河(淄脉河)全长约128公里;二是南京大学地理系在1965年《黄河三角洲海岸地貌调查阶段报告》中根据“贝壳堤”的分布确定古海岸线的位置是大河口堡、套尔河堡、小沙、鲁西坨子、大洋铺、十二村、李家坨子、二八闾、老爷庙、毛丝坨、十五村、青坨子、羊角沟东北部。两条岸线中,前者有陡弯数处,后者较平缓。
二、1855年后海岸线变化
黄河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再度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时,两岸尚无堤防束水,荷泽、东明一带经常泛滥四溢,大量泥沙沉积泛区,进入河口地区的水流含沙量少,将狭窄的大清河道拓宽刷深。清光绪元年(1875年)前后,自上而下修筑的沿河堤埝渐趋完固,进入河口地区的水沙数量剧增到难以容纳的程度,遂出现“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的局面①,开始大量淤积沉淀的造陆阶段,使海岸线不断向前推进。黄委会水科所、设计院、济南水文总站等单位,根据有关文献及海图、地形图、航摄照片、卫星遥感、钻探资料及实地调查报告,编绘出1855、1909、1947、1954、1959、1961、1964、1976和1983年的高低潮线位历史变迁图,其范围是套尔河以东、淄脉沟口以北。分析计算确认:1855-1985年间,尾闾河段实际行水96年,海岸线平均向前推进28.5公里,推进速率0.30公里/年。其中,1947年前以宁海为顶点的三角洲计算岸线长105公里,平均推进13.3公里,实际行水57年,岸线延伸速率0.23公里/年;1947〜1985年以渔洼为顶点、挑河至宋春荣沟之间的小三角洲计算岸线长80公里,平均推进15.2公里,实际行水39年,延伸速率0.39公里/年。最近几年人工控制河口摆动范围,淤积影响宽度仅30公里左右,岸线推进速率增大到1.6公里/年 (参见表4—5)。
1983-1986年山东省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对黄河口区(第三调查区)西起套尔河口,南至淄脉沟口,地理座标东经118°20′〜119°30′,北纬
近代黄河口海岸线延伸统计表 表4—5
说明:(1)1855〜1947年造陆面积包括蚀退影响在内。
(2)前三沟、后三沟均指甜水沟、宋春荣沟、神仙沟而言。
(3)岸线长度分别按宁海和渔洼为顶点的大、小三角洲计。
(4)岸线推进以净造陆面积计算。
37°20′〜38°30'范围的研究认为海岸线推进分三个阶段:
(一)1855-1934年是海岸线大范围推进阶段。最快是神仙沟五号桩区域。1934年的海岸线超过1855年的10米等深线,平均淤进3公里,最远处达8公里。其次是挑河及套尔河口,1934年的海岸线推进到1855年的7~8米等深线附近。再次为甜水沟口附近,1934年的海岸线推进到1855年的5米等深线。宋春荣沟以南岸线推进幅度逐渐变小,1934年的海岸线仅到达1855年的干出线(滩),广利河口一带还有轻微的蚀退。已勘探开采的义和庄、义北、义东、渤海、孤岛、孤南、垦西、垦利、河滩等油田都是这一时期相继淤成的陆地。
(二)1934〜1959年是西北蚀退、东南淤进阶段。神仙沟五号桩区域1959年的干出线(滩)已经接近1855年的15米等深线,最大淤积厚度16.4米;5米等深超过1855年的15米等深线。甜水沟区域1959年的海岸线接近1934年的10米等深线,最大淤积厚度13.1米;干出线超过1934年的10米等深线。宋春荣沟以南淤进幅度逐渐变小,1959年的海岸线超过1855年的干出线,接近5米等深线;淄脉沟口外则为轻微蚀退。神仙沟以西陆地和浅滩蚀退,挑河附近显著蚀退,湾湾沟区略有蚀退。埕东、桩西和五号桩等油田处在潮滩附近。
海区的冲淤与1934年前相反,冲刷的海域基本变为淤积,淤积的海域基本转为冲刷。神仙沟五号桩海区受黄河入海的泥沙影响,使1934年水深为19.8米的海区几乎被填平而处在干出线附近。这是1855年以来淤积速率最快的时期。在停水30年以上的西部海域,10米等深线以外亦呈明显淤积,最大淤积厚度2.4米。
1855-1959年东北部海域15米等深线附近及其以浅海域为淤积;15〜20米海域是冲刷;20米以深海域基本上是淤积,仅局部有冲刷。甜水沟以南海区1959年10米等深线以浅范围内淤积,以深海区则冲刷。淄脉沟口外1959年5米等深线以深海域仍是冲刷。
(三)1959-1984年是以渔洼为顶点的三角洲持续淤进阶段。淤进最迅速的是刁口河海域和清水沟海域。1984年的海岸线接近1855年的15米等深线,在干出线以内区域普遍淤厚11-14米,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淤厚8〜12米,1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淤厚4〜8米,1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淤厚2〜5米。现行河口东北部20米等深线附近冲刷。20米等深线以外又有淤积,厚1~3米。以往迅速淤进的神仙沟五号桩海域,除1973〜1974年因刁口河流路入海口门摆动到神仙沟受影响外,累计停水18年,淤进速度较慢,1984年的5〜15米等深线相应超过1959年的各等深线。埕东、桩西、五号桩、长堤、孤东、一棵树、红柳等油田系此阶段淤出的陆地。湾湾沟区域已半个世纪不受泥沙直接影响,海岸线附近明显蚀退,1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略有冲淤,基本稳定。宋春荣沟以南近30年没有受泥沙直接影响,海岸线至10米等深线略有冲淤,变化不大。
综上所述,1855年以来近代海岸线受自然夷平规律的控制,基本上沿顺直趋势发展。表4—6以1855年海岸线为起点罗列了神仙沟口、湾湾沟附近、永丰河口以南不同深度的淤进距离和速率。由于海岸线淤进中又表现以淤 (进)为主、冲(退)淤(进)交替的过程,表4-7罗列了潮滩外冲淤变化的情况。
1855〜1984年黄河口不同深度淤进表 表4—6
1855〜1984年黄河口海域冲淤量统计表 表4一7
三、海岸延伸特征
(一)叶瓣进积模式:黄河以高含沙量著称于世,高速沉积和频繁决溢导致尾闾河段经常摆动,流路多变。对照流路变迁年序,每次流路变迁均在河口留下一片状如叶瓣的泥沙堆积体。这是由于每条流路改道之初先沿着三角洲凹岸入海。将凹湾填平之后,又向海域淤进凸出。后期发生自下而上的出汊摆动时,又将泥沙向左右两岸扩散堆积,使叶瓣体进一步扩大。经过10多年的淤积延伸,新的叶瓣总是超过旧的叶瓣。如此循环往复,叶瓣之间相互套迭,使三角洲地面抬高,海岸线普遍推进,渐次外延。
(二)拦门沙坝:挟沙水流到河口与潮流引起的底沙再悬浮相遇,形成一个高含沙区(亦称最大浑浊带),在两水交汇、势能锐减和化学因素的作用下,高含沙区内的泥沙大量沉淀,堆积成一道顺河长7公里左右的拦门沙,横亘在口门潮流段内。其纵剖面形态表现为背坡(向河)较缓,前坡(向海)较陡(1983年9月拦门沙前坡比降达8.7‰)。靠近陡坡的拦门坎宽1〜2公里,坎顶水深随潮汐变化不定,低潮时近乎裸露。随着泥沙不断堆积,拦门沙每年向前推进约1.8〜3.5公里。1984年山东省海岸带调查时先后在5月和7月两次实测,拦门沙顺河长4公里,起点距清7断面14公里(参见图4—3),坎顶平均高程﹣0.5米(黄海基面,下同)。1987年9月实测拦门沙长度5.5公里,起点距清7断面17公里,坎顶高程一0.1米。两次测量间拦门沙前沿向前推进4.5公里,平均每年推进1.32公里。
河口拦门沙使入海流路常处半堵塞状态,阻碍泄水排沙。枯水季节不断沉积淤高,洪水季节造成滞流壅水。引发出汊摆动后,又在新口门处堆积新拦门沙。清水沟行水近13年,口门变动较大的13次(参见表4—1)。在拦门沙垂向淤积和横向摆动过程中,海岸线逐步外延,导致侵蚀基面升高,是河口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河口沙嘴发育:其基本过程表现为:初期(游荡散乱阶段)纵向与横向扩展均相对突出;中期(单一深槽阶段)很少漫滩淤积,泥沙主要呈纵向向海延伸;后期(出汊摆动阶段)类似初期状态。据水文资料计算,一条流路的沙嘴延伸速率多年平均为2.3-3.3公里/年。刁口河流路初期沙嘴延伸速率3.18公里/年;游荡阶段为1.85公里/年;归股单一阶段为1.33公里/年;出汊摆动阶段复又增大到1.9公里/年。清水沟流路的沙嘴在1983年9月已突出平均岸线16公里,河长延伸速度达3.55公里/年。当河口沙嘴突出到原海岸线以外时,在水流、风浪、潮流的强烈作用下虽能将30〜40%的泥沙输往深海,余沙仍以原沙嘴为基础继续向前方和两侧漫延堆积。随着诸流路的纵向延长和横向摆动,沙嘴交互套叠,把海岸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
黄河口拦门沙淤进情况图 图4-3
(四)岸线蚀退:黄河口是陆相沉积的淤泥质海岸。当流路发生变迁后,断流的岸段失去陆源物质补给,在海洋动力作用下发生蚀退。据黄世光、王志豪等计算统计:1855〜1984年黄河口共造陆2770.4平方公里,同期蚀退240平方公里,占造陆面积的8.66%。黄委会水科所、济南水文总站等单位刊布资料:1954〜1975年间,河口在80公里范围内淤积造陆786平方公里,同期蚀退面积208平方公里,占造陆面积的26.5%。由于各岸段行河时间长短不同,淤进蚀退亦不尽相同。套尔河口至挑河和宋春荣沟至淄脉沟岸段由于多年不走河,属于相对稳定岸段。挑河至宋春荣沟岸段,半个多世纪以来都在行河,岸线虽然有进有退,仍以淤进为主。刚开始行河和停止走河的岸段淤进和蚀退都很明显。1960年8月由神仙沟改道汉河后,至1963年新河口附近造陆124平方公里,老河口附近蚀退56平方公里,占造陆面积的45%;1964年初由汊河改道刁口河,至1975年新河口造陆500平方公里,老河口蚀退166平方公里,占同期造陆面积的33%(参见表4—5)。
(五)河口沙嘴延伸和海岸线相继全面推进,对上游河道冲淤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但有很大不同。沙嘴延伸引起的河段增长使河道产生溯源淤积的时段短,范围小;河口摆动后引起沙嘴变动又使河段缩短而引起溯源冲刷,亦是时段短、范围小。两者影响上界都在泺口以下。在此范围内,河口口门频繁变化使河段呈间歇性增长或缩短,河床纵剖面也呈间歇性升高或下降。三角洲岸线普遍外延引起的河段增长不但使河口河床抬高,水位上升,而且也向上传播,影响范围超过泺口。王恺忱、周志德在《黄河河口演变规律及其对下游河道影响》一文中指岀:1950〜1975年间,夹河滩和高村以下河段3000立方米每秒的年均水位升高2.07〜2.38米;艾山以下河段在1954-1975年间累计普遍升高2.10米;与同时段河口延伸引起的水位升高值2.13米相一致,近乎平行升高。花园口至利津河段比降30余年来呈变缓趋势等情况,亦证明黄河下游是属于溯源淤积性质,认为产生淤积的主要原因与河口延伸引起的基准面相对升高有关。
河口演变对上游河道的影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黄河三角洲岸线各段变化差异很大,不是普遍向海内均匀淤进。1954年至今,河长尚未达到稳定延长,河道还远未达到平衡状态,仍处于强烈堆积状态。淤积原因主要与来水来
黄河河口工程分布图
沙条件有关,还是自上而下的沿程淤积。河口淤积延伸也受到河口改道引起的溯源冲刷制约,但产生溯源淤积向上游的影响范围有限。从1973-1983年铁谢至一号坝各站水位升降情况(参见表4—8)还看不到由于河口淤积延伸引起下游河道平行淤高的现象。
1973〜1983年黄河下游各断面3000立方米/秒水位升降表 表4—8
注:“一”号表示水位下降值。
总之,近代河口海岸线沿着强烈淤积→强烈蚀退→中度蚀退→轻微蚀退 →相对稳定的格局演变。纵向是上冲下淤,平面上是此冲彼淤,有进有退,进退交替,进的范围小而速率大,退的范围大而速率小。
第三节三角洲演变
一、三角洲沿革
黄河三角洲是以巨量泥沙堆积在入海口附近而形成的扇面状陆地。对其扇面范围和顶点位置有不同解释。史前时期的黄河下游即以河南省孟津为顶点,在北至天津大沽口、南至淮河入海处的广袤地带纵横奔流,迁徙无定,波及冀、鲁、豫、皖、苏五省20多万平方公里。因多次改道迁徙和频繁决溢沉积塑造的广大地区,称古代三角洲。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又塑造岀一个小范围的三角洲,即“利津县城以东黄河口部分地区。”①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利津宁海(今垦利)为顶点,北起套尔河口、南至淄脉沟(南旺河)口的扇状地带称近代黄河三角洲,至1984年面积已逾6000平方公里(参见表4—9)。
黄河三角洲各类土地面积表 表4一9
建国后,河口地区经济开发逐步加快。在人为控制下将河道摆动顶点移至垦利渔洼(左岸利津四段村)附近,北至挑河,南至宋春荣沟之间的三角洲扇形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称现代黄河三角洲(见图4—4)。
二、洲面淤积特征
据利津水文站1949-1988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输至河口地区的泥沙年均10.03亿吨。进入河口地区的泥沙有24%左右沉积在大沽零米线(陆地)以上,有40%左右沉积在零米线以下的滨海区,其余被海流输至深海。刁口河流路行水12.5年,来沙总量135.2亿吨。其中的21.6%沉积在陆上抬高洲面,44.1%延伸沙嘴填海造陆,34.3%被输往深海。在尾闾流路频繁变迁的过程中,以自上而下、左右交替的形式,平均每年填海造陆3〜4万亩的速度,形成由若干大小沙嘴和海湾联接、外沿曲折、突向东北的扇状陆地。黄河自1855〜1955年在近代三角洲扇面上发生过50多次决口或改道,洪流四溢,非冲即淤。为避水患而修筑的堤埝纵横交错,围堵拦截,形成岗坡沟洼相间的复杂地形和起伏涟漪的微地貌。故道地形相对较高,故道相距较远者,其间多为洼地。故道相距较近,走河时间较长而又无堤防者,高地连成一片。三角洲中部行河时间较长,地面相对较高,呈现中间隆起的拱形曲面。
沉积在洲面上的泥沙,大致分为沙壤土和粘土。故道主流处地表均露沙土,故道两侧滩地多为沙壤粘土互层,河间洼地逐渐过渡为较厚的粘土层。
河口相对稳定海域条件变化不大时,泥沙颗粒粗细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在横向上,河口沙嘴部位颗粒较粗,两侧较细;在纵向上,陆地和滨海区前沿顶部较粗,愈向外海愈细。利津水文站多年测验成果(参见表4—10),输至河口地区的泥沙多为悬移质中的冲泻质,年均中数粒径d50在0.0064〜0.038毫米之间,其中d50<0.025毫米的泥沙,占总量的50%强;d50<0.010毫米的极细沙占总量的25%。因大部分细沙易被海流挟入深海,沉落在三角洲岸坡(包括水下部分)上的泥沙颗粒相对粗化。对浅海底质资料分析表明,三角洲岸波上的泥沙分布亦有分选现象。通流海域5米等深线以内d50>0.03毫米,10米等深线以外d50<0.02毫米,且有很大范围d50<0.01毫米,是径流泥沙的扩散区域。不通流海域泥沙分布为上部粗,下部细,但都是d50>0.03毫米。
每条流路的泥沙沉淀表现为陆上粗沙比例大,细沙比例小;水下则相反。刁口河流路的粗颗粒泥沙中70%淤积在陆上沙嘴顶部,仅有7.5%能被输送到海岸线坡脚以外。细颗粒泥沙中72.4%被输送到沙嘴前沿以外。流路发育
利津贴(刘家夹河)逐年水沙特征值统计表 表4-10
(续表)
(续表)
的各个阶段,泥沙分布也不同。改道初期,几乎全部来沙都淤积在滨海区时,水上部分细沙比例相对较大;当沙嘴逐渐稳定和外突时,细颗粒泥沙的绝大部分被输至深海,陆上存留比例甚少。还有一部分滞流在沙嘴两侧的凹湾处,形成以极细物质为主的浮泥区,范围约几平方公里,浮泥厚1〜5米不等,渔民称 “烂泥湾”,是良好的避风场所。
另据水文部门测验证明,由于黄河有水沙异源的情况,在不同时段和地区的水沙组合对河口泥沙沉积有很大影响。年度之内,汛期悬移质组成一般较细,非汛期较粗。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来沙与龙门至三门峡区间来沙,粗细程度亦有差异。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与改建前后比较,来沙粗化明显。据1950〜1975年资料统计,三门峡水库建成前(1955〜1959年),粒径小于0.025毫米的泥沙占总量的64.2%;水库建成运用后(1960〜1965年)占55%;水库改建期间(1967〜1973年)占44.9%;水库恢复正常运用(全年控制)后(1974〜1977年)占45.8%。清水沟流路行水后,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改变为“蓄清排浑”,泥沙颗粒大于0.025毫米的床沙质含量占总量的61.5%。
三、三角洲开发
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古三角洲边缘已建置永利镇等较大聚落,定居之民分布在陆地或沿海一带从事农桑或捕捞。随着人口繁衍生息,数量增加和经济发展,至金明昌三年(1193年)十二月永利镇升为利津县置,成为三角洲边缘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之一。其后,三角洲腹地成为大清河入海流经之地,水流清澈,河槽深邃,利津城南土地相继脱盐变为宜耕区,农桑发展加快。城北土地靠近滨海,含卤重,不宜农作,却促发盐业、渔业和海关运输业及商业的兴起,先后形成丰国(今汀河)、永阜、宁海等较大村镇,出现“巨海枕其北,清河绕其东,南有桑枣之饶,西通舟车之利”①的繁华昌盛情景。
明代初期,山西洪洞及直隶枣强等地大量移民迁至三角洲定居,垦植面积迅速增加。至清代中叶,三角洲顶部的农业和滨海处盐业、浅海区渔业、铁门关及城镇商业、水陆交通业等都相当发达。“昔济水由利津入海,名曰大清河,河门通畅,南北商船由渤海驶入河口在铁门关卸载,由河内帆船输运而上。彼时物品云集,商人辐凑,此为商业最盛时期”。①永阜、丰国、富国等地成为山东省大型盐场。清康熙年间奖励生育,人丁剧增,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利津县册报人口已达4.78万余户,近27万人,拥有土地45万余亩。仅永阜盐场即有滩池420付,产盐为8场之冠。除在鲁西北销售外,还远销河南、江苏等地。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初时沿河堤防断断续续,东明、荷泽一带时常泛滥成灾,滞洪留沙,近海地区水害尚不严重。至清光绪九年(1883年)利津以上堤防完整,河口地区水患加重,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先后造成大清河航道淤塞,铁门关码头废弃,各大盐场被毁。繁华数百年的近海地区经济逐渐萧条。但在不景之中,黄河却以独特的水沙在新老套迭的河道上轮回变迁,淤海造陆,再度使三角洲面积大幅度扩展。清光绪末年,宁海以上堤防亦具相当御水能力,决溢较少,农业已见复兴。宁海以下新淤陆地上,灶户盐民开始改营农作。民国初期,政府鼓励垦荒,邻县穷苦农民先后进入三角洲内拓地垦荒,仅凭县府颁发的领单验单即可尽力粗放耕耘,每亩收费甚微,使三角洲近海地区农业初见生机。民国15年(1930年),韩复榘部五十九旅进洲屯垦;民国24年(1935年),鲁西南灾民4200余人由政府组织迁居河口择地栖息,进一步加速了近海地区农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黄河三角洲成为清河区、渤海区革命根据地。民国30年 (1941年)中共渤海区委设置垦区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民国32年(1943年)建置垦利县人民政府,使三角洲再度出现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繁荣阶段。民国31年(1942年)至34年(1945年)间,由人民政府安置在垦利县的移民近2万户,约11万人,垦植土地近45万亩。盛产的谷物、豆类、棉花、油脂、酱菜等农副土特产品,不但保障解放区人民的物质需要,亦成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
建国后,在兴修水利设施、改革耕作习惯、推广科学种植、引进机械电力的基础上,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林、牧、副、渔等业。1949年后,又组织四次向三角洲迁民,至1960年,利津、垦利两县共安置移民5万余人。自1950年起,相继组建广北、五一、黄河、渤海、海滨、联合、共青团、同兴、淄脉沟、青坨等中小型国营农垦、劳改场,济南军区军马场及一千二(渤海)、孤岛等林场。1961年始,至1986年底,在潮河至永丰河约5000平方公里内相继探明油田23处,地质储量可观,年生产能力近1500万吨。以石油化工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开始萌发壮大,带动其他行业竞相起步,使三角洲面貌焕然一新。
1983年东营市建制后,制定“油洲加绿洲”的战略开发规划,以能源化工和农林牧渔盐业综合发展为目标,使黄河三角洲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和商品粮生产基地。现代工业、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交通运输、商业供销、文教科技、农田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亦初具规模。三角洲经济进入全面振兴、综合开发的新时期(参见图4—4)。
历史上,黄河三角洲曾经保持丛林密布、草木繁茂的自然生态环境,植被覆盖面积达60%以上,1953年仍达20.93%。60年代以来,毁林开荒、滥垦酷牧,至1981年植被覆盖面积仅有2.93%。经有关部门和人士疾呼,引起各级政府重视,遂提倡植树造林,播种草场,绿化状况已见转机。至1987年底,植被覆盖回升到近60万亩,约占三角洲面积的7%。
一、变迁过程黄河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以来,因人为或自然因素在宁海为顶点的三角洲扇面上决口、分汊、改道频繁。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调查统计,决口改道达50余次,其中导致尾闾流路变迁9次(参见图4—1)。各条流路行水情况如下:
(一)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铜瓦厢三堡(今东坝头)决口。溃水至山东东阿张秋镇穿运河入大清河河道后,流经平阴、东阿、齐河、济南、济阳、齐东、惠民、高苑、蒲台、滨州等地至利津县沿宁海、十六户、薄家庄、台子庄、韩家垣在铁门关以北、肖神庙以下之二河盖牡蛎嘴入海。历时34年,实际行水19年(其余时间系因上游傍决改道而干河,下同)①。
(二)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韩家垣漫溢决口,溃水在老鸹岭附近分汊后,又在付家窝附近合股归一,经四段及杨家嘴至毛丝坨以下(今建林东)入海。山东巡抚张曜以其地距海较近而不堵塞决口,在两岸各筑新堤三十里束水中行,历时8年,实际行水5年又10个月。
图4一1黄河河口流路变迁图
(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北岭、西滩两地漫决。不久,西滩口门渐被淤塞,大溜全注北岭,溃水由薄家庄南东流,过集贤村转向东南,经左家庄、永安镇、老十五村由丝网口(今宋家坨子)以下团坨子以北入海;另有支汊一股在乱井子(清河村旧址)西北分流,又在羊栏子与三十八户之间合一,历时7年,实际行水5年又9个月。
(四)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薄家庄决口,河经青边岭、虎滩嘴、流口、薄家屋子、义和庄入徒骇河下游绛河故道,在太平镇以北老鸹嘴入海。13年后此道淤塞,又在太平镇改行东北经大洋铺、中和堂在车子沟入海;另由虎滩嘴东南、陈家屋子北分出岔河,经大牟里、小牟里、四扣在刘家坨子、韩家屋子以北面条沟(今挑河)入海。民国14年(1925年)又在虎滩嘴分岔向西北岀沾化入无棣由套尔河入海。此次北流入海历时22年,实际行水17年又9个月 (按:有的文献曾以太平镇改道前后作为两次变迁记载)。
(五)民国15年(1926年)6月,八里庄以北(吕家洼)决口,向东北经丰国镇(今汀河)沿铁门关故道及沙子头(刁口河)入海,历时3年。
(六)民国18年(1929年)8月,纪家庄盗掘大堤成口东泄,河经义和村、东张、西双河、民丰、一村等地,初由南旺河(今支脉沟)入海,7、8个月后又在乱井子以南改行东南,至民丰以北入第3次行水故道;一年后又在永安镇以南改向,经下镇由宋春荣沟入海;行水两年后,复在永安镇西南改向青坨子入海。历时5年,实际行水3年又4个月。
(七)民国23年(1934年)8月,合龙处(今涯东村)决口,溃水向东漫流,先由毛丝坨以北老神仙沟入海;后又形成神仙沟、甜水沟、宋春荣沟三路入海形势。民国27年(193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军队在郑州花园口掘堤,黄河改由徐淮故道注入黄海,山东河竭。民国36年(1947年)3月,花园口口门堵复,黄河重归山东仍循甜水沟(过水约七成)、神仙沟(过水约二成)、宋春荣沟(过水近一成)分注渤海。历时19年,实际行水9年又2个月。
(八)黄河归故后的三条入海路线以甜水沟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沟淤积延伸,行程加长,比降变小(平均万分之一),河形蜿蜒曲折。相对神仙沟行程较短,比降较大,过水比例逐渐增加,并在小口子村附近形成两河弯顶相向发育,至1953年两弯顶相距仅95米,有自然沟通之势。遂因势利导于当年7月在两弯顶之间开挖引河,促成神仙沟独流入海。历时10年又5个月。
(九)1964年凌汛,罗家屋子以下河道卡冰壅水漫滩,危及河口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查勘研究,山东省委授权由惠民地委决定,于1964年1月1日在罗家屋子爆破民坝分泄凌洪,由草桥沟、洼拉沟入刁口河漫流归海。5月,新流路过水六成以上,终成改道刁口河。行水12年又5个月。
(十)1976年5月,经多年筹备改道清水沟计划付诸实施,在罗家屋子进行人工截流成功,炸开西河口引河挡水坝,改由清水沟入海。迄今已逾12年,仍在继续行水。
二、现行流路演变
清水沟是神仙沟与甜水沟之间的洼地,长27公里,地面高程较两侧地势低1.5-4.0米,入海口位于两故道沙嘴间的凹湾处。
(一)河势变化(见图4-2):清水沟开始行河时水流沿引河下泄、顺自然地势向东入海,河面宽2〜3公里,主流位置居中偏南,河势散乱。清4断面以上四股水流显见,但主流过水部位偏重在南防洪堤附近,引起十八公里堤身靠溜成险。1978年春抢修护林挑水坝,截堵南部三股水道,十八公里险工溜势上提变缓,水流并为一股。清4断面以下经历四个阶段,即:1976〜1980年为淤滩造床阶段,最初漫流入海,尔后河势游荡,不断产生汊河,主溜变化不定,入海口门摆动频繁,最大摆动距离达23公里(参见表4-1),沙嘴延伸迅速;1980-1985年,河势渐趋稳定,主槽成单一状态,滩槽高差由0.74米增加至2.35米;1985〜1987年,河道淤积,清7断面以下尤重,拦门沙明显,顺河长4〜5公里,垂直河宽7公里,入海口门不畅;1988年起,为稳定现行流路,改善河口地区防洪(凌)的不利形势,实施调整入海口门,清理河道阻水障碍,修筑导流堤,在尾闾河段进行机船疏浚拖淤和截支强干,同时在西河口至十八公里间修建控导工程,对稳定河势、通畅河门起到一定作用。西河口以下出现单一顺直河槽,10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一般滩唇出水高0.5米左右。清8断面上下河槽宽800米左右,无分汊支沟,低潮时拦门沙水深仍达1.3米左右。
(二)河道冲淤:改道当年水量偏丰,沙量偏枯,利津站最大洪峰8020立方米每秒历时5天,平均含沙量仅12公斤/立方米。艾山以下河道普遍发生沿程冲刷。因改道引起的溯源冲刷也较显著。其后,河口不断淤积延伸,河长有所增加,但因河势发展较好,利津至西河口河道主槽仍保持冲刷(参见表4—2)。西河口以下虽以淤积为主,却在淤滩造床中形成单一主槽。据1987年汛前实测,利津以下河道总长为104公里,比刁口河流路末期河长尚短7公里。利津至西河口河段河床平均高程低于改道前0.31-1.08米;与改道前的3000立方米每秒同流量水位相比,西河口站低0.54米,一号坝站低0.56米,利津站低0.51米。西河口以下河道主槽高程与改道前相比,清1至清2断
黄河清水沟流路河势变迁图图4-2
清水沟流路河口延伸摆动表 表4-1
注:①1976年6〜10月延伸长度11公里;1976年10月〜1978年10月延伸长度5公里。
②“一”为蚀退。
清水沟河道主槽冲淤变化表 表4—2
注:正数为淤积,负数为冲刷。
面低1.0-0.6米,清3至清7断面淤高1.1-1.4米。滩地平均淤高:清1断面1-1米,清2至清6断面2.23-2.73米,清7断面达4.3米。
随着流路冲淤塑造发展,河床纵剖面形态亦相应的自动调整。1986年汛前利津至西河口比降约0.8‰,西河口至清7断面约1.1‰,改道点以下河床仍陡于改道点以上,但差值很小。在来水来沙的作用下,河床横剖面形态亦向窄深方向发展。西河口以下河道过水断面的变化是:清10断面以上主槽宽度由大变小,1976年主槽宽度1206-2980米,1986年缩窄到1000米左右;平槽流量下的断面平均水深由小增大,1976年0.84〜1.92米,1986年后达到1.97〜3.32米。
(三)河口淤积:改道清水沟流路初期入海位置多变,在较大范围内促使岸线普遍外延。1980年后,河道归顺单一,无大出汊摆动,沙嘴呈单一集中形式淤进,宽度在20〜30公里之间,2〜12米水深区的淤积量占观测范围内总淤积量的81%(浅海淤积总宽度为53公里)。1984年实测,浅海水下岸坡形态 (又称水下三角洲)大体分为:0〜2米等深线之间的顶坡段,比降4〜9‰;2〜12米等深线之间的前坡段,比降30〜35‰;12米等深线以下的尾坡段,比降2〜3‰。据统计,采用一2米高程线作为造陆面积的界限时;清水沟行河的1976〜1985年间,河口造陆面积累计为406平方公里,年均43.5平方公里①,入海1亿吨泥沙,平均造陆7.15平方公里。输送至河口地区的泥沙,淤积在河道和12米等深线以内海区的约占利津站输沙总量的80%左右;输至12米等深线以外的约占20%左右。近几年水文测验资料,河口沙嘴突出后,最大潮流速达2米/秒左右,比莱洲湾原潮流速值0.6米/秒显著增大;潮流速方向为涨潮向南,落潮向北,与河口射流方向大体垂直,有利于泥沙向河口两侧的输送。
三、变迁规律
50年代,黄委会水科所及河口水文站等单位开始对1855年以来近口流路变迁进行调查考证。其后,随着资料不断积累和认识逐步加深,特别对神仙沟、刁口河、清水沟3条流路的原型观测成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后,认为河口流路变迁基本遵循以下几点规律:
(一)淤积延伸摆动改道是黄河口自然演变的基本形式。每年3〜7亿吨泥沙在河口堆积后,相应改变河流侵蚀基准面高程,导致河床比降变缓,水位升高。达到一定程度后,近口流路势必自寻最小阻力捷径入海,孕育一次尾闾改道。在水沙条件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条流路的自然演变周期大体为10年左右。
(二)每条流路行水期间,平面河型演变过程为:改道初期游荡散乱→归股→单一→弯曲→出汊摆动→出汊点上移→再改道散乱。以上发育过程完成后,构成一次“小循环”。几次不同入海流路的“小循环”在三角洲洲面上从中部开始,先南后北横扫一遍后,构成一次“大循环”,三角洲岸线则普遍向海推进一次,导致河口水位进一步上升。
(三)每次尾闾变迁对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都产生直接影响。一般表现为初期流程缩短,比降变陡,改道点以上发生溯源冲刷,上界可抵刘家园或泺口,距改道点200公里左右。维持几年的低水位状态后,又开始溯源堆积或沿程堆积,河床高程平行上升,同流量水位再度升高,成为下一次流路变迁的前兆(参见表4—3) 。
(四)尾闾流路变迁可以暂缓河口地区防洪防凌压力。河口地区地势低平坦荡,防洪设施简陋,伏汛、凌汛涨水漫滩出险较多,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很大,防洪防凌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河口流路发生变迁后,河道边界条件有所改善,口门较为通畅,泄洪(凌)排沙能力增大,一般可以维持几年的低水位状态,减少洪、凌漫滩机遇,缓解防洪防凌压力。如1953年神仙沟独流入海后,不仅战胜1954年出现的7220立方米每秒、1957年岀现的8500立方米每秒等较大洪水,而且战胜了1958年岀现的10400立方米每秒大洪水。1964年元月改道刁口河以后,不几天便缓解了当时的凌汛危机。1975年汛期最大洪水仅6500立方米每秒,且有渔户村分洪口门过水,西河口水位仍然接近10米,河口地区防洪处处吃紧。但在1976年实施改道清水沟计划以后,河口地区同流量水位大幅度下落,当年岀现8020立方米每秒洪水也安然渡过。因此,在河口水沙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合理安排入海流路,实行有计划的人工干预,是解决河口摆动改道与工农业生产矛盾、减轻重大洪(凌)灾损失的有效措施(参见表4—4)。
河口变化对下游河道影响的幅度、范围及历时表 表4-3
人工干预河口改道情况表 表4-4
第二节海岸线
一、1855年前海岸线形成
黄河三角洲在古地质构造上是河淮凹陷平原的一部分。中新世中期,平原整体下陷,与当时的胶辽古陆解体,利津一带处在渤海凹陷中心的南沿。第四纪(大约200万年前开始)以来,自孟津脱谷而出的黄河及源自太行、燕山之麓的海河水系携带大量泥沙南北交替淤积,逐渐填充了长期以来的地壳下沉而成陆,沉积物厚达500-800米。大约四千年前,冲积扇延伸到泺口以东。至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年前后),利津城西、城南已成陆地凸入海中①,是西周至西汉时期先后称名齐地、千乘郡、蓼城县、湿沃县的地方。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今濮阳境)决口改道,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时,自荥阳筑堤千里,导河由千乘入海后,以利津城附近为起点向东、向北展开造陆。西汉至南北朝期间城西地区变化不大。隋至唐末(公元581-907年)的三百多年间,利津一带海岸线外延约30余里,今王庄、盐窝、北岭、董集、坨庄等处均成陆地。至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城东增至60余里。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城北又增至60余里,海岸线推进到铁门关(今前关村)一带,虎滩、汀河、陈庄、集贤、民丰等地退海成陆②。
金明昌五年(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今中牟、延津一带),形成南北分流,南河夺泗入淮,北河夺大清河(又称北清河)至利津一带入海,继续造陆。至明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主修太行堤遏制北流,全黄入淮归注黄海为止,历时300余年,海岸线又推进30余里至老爷庙一带。太平、义和、六合、付窝、西宋、永安等地相继脱海。此后,黄河之水客串利津仅属偶见,造陆剧缓,最终形成现黄河口海岸线。对此古海岸线位置的确定:一是黄委会前左河口水文实验站根据实地调查海堡分布及有关历史文献,参考航测照片判读确认的大体走向是由徒骇河(即套尔河)起,经耿家局子、老鸹嘴、大洋铺、北混水旺、老爷庙、罗家屋子、友林等地附近,至南旺河(淄脉河)全长约128公里;二是南京大学地理系在1965年《黄河三角洲海岸地貌调查阶段报告》中根据“贝壳堤”的分布确定古海岸线的位置是大河口堡、套尔河堡、小沙、鲁西坨子、大洋铺、十二村、李家坨子、二八闾、老爷庙、毛丝坨、十五村、青坨子、羊角沟东北部。两条岸线中,前者有陡弯数处,后者较平缓。
二、1855年后海岸线变化
黄河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再度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时,两岸尚无堤防束水,荷泽、东明一带经常泛滥四溢,大量泥沙沉积泛区,进入河口地区的水流含沙量少,将狭窄的大清河道拓宽刷深。清光绪元年(1875年)前后,自上而下修筑的沿河堤埝渐趋完固,进入河口地区的水沙数量剧增到难以容纳的程度,遂出现“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的局面①,开始大量淤积沉淀的造陆阶段,使海岸线不断向前推进。黄委会水科所、设计院、济南水文总站等单位,根据有关文献及海图、地形图、航摄照片、卫星遥感、钻探资料及实地调查报告,编绘出1855、1909、1947、1954、1959、1961、1964、1976和1983年的高低潮线位历史变迁图,其范围是套尔河以东、淄脉沟口以北。分析计算确认:1855-1985年间,尾闾河段实际行水96年,海岸线平均向前推进28.5公里,推进速率0.30公里/年。其中,1947年前以宁海为顶点的三角洲计算岸线长105公里,平均推进13.3公里,实际行水57年,岸线延伸速率0.23公里/年;1947〜1985年以渔洼为顶点、挑河至宋春荣沟之间的小三角洲计算岸线长80公里,平均推进15.2公里,实际行水39年,延伸速率0.39公里/年。最近几年人工控制河口摆动范围,淤积影响宽度仅30公里左右,岸线推进速率增大到1.6公里/年 (参见表4—5)。
1983-1986年山东省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对黄河口区(第三调查区)西起套尔河口,南至淄脉沟口,地理座标东经118°20′〜119°30′,北纬
近代黄河口海岸线延伸统计表 表4—5
说明:(1)1855〜1947年造陆面积包括蚀退影响在内。
(2)前三沟、后三沟均指甜水沟、宋春荣沟、神仙沟而言。
(3)岸线长度分别按宁海和渔洼为顶点的大、小三角洲计。
(4)岸线推进以净造陆面积计算。
37°20′〜38°30'范围的研究认为海岸线推进分三个阶段:
(一)1855-1934年是海岸线大范围推进阶段。最快是神仙沟五号桩区域。1934年的海岸线超过1855年的10米等深线,平均淤进3公里,最远处达8公里。其次是挑河及套尔河口,1934年的海岸线推进到1855年的7~8米等深线附近。再次为甜水沟口附近,1934年的海岸线推进到1855年的5米等深线。宋春荣沟以南岸线推进幅度逐渐变小,1934年的海岸线仅到达1855年的干出线(滩),广利河口一带还有轻微的蚀退。已勘探开采的义和庄、义北、义东、渤海、孤岛、孤南、垦西、垦利、河滩等油田都是这一时期相继淤成的陆地。
(二)1934〜1959年是西北蚀退、东南淤进阶段。神仙沟五号桩区域1959年的干出线(滩)已经接近1855年的15米等深线,最大淤积厚度16.4米;5米等深超过1855年的15米等深线。甜水沟区域1959年的海岸线接近1934年的10米等深线,最大淤积厚度13.1米;干出线超过1934年的10米等深线。宋春荣沟以南淤进幅度逐渐变小,1959年的海岸线超过1855年的干出线,接近5米等深线;淄脉沟口外则为轻微蚀退。神仙沟以西陆地和浅滩蚀退,挑河附近显著蚀退,湾湾沟区略有蚀退。埕东、桩西和五号桩等油田处在潮滩附近。
海区的冲淤与1934年前相反,冲刷的海域基本变为淤积,淤积的海域基本转为冲刷。神仙沟五号桩海区受黄河入海的泥沙影响,使1934年水深为19.8米的海区几乎被填平而处在干出线附近。这是1855年以来淤积速率最快的时期。在停水30年以上的西部海域,10米等深线以外亦呈明显淤积,最大淤积厚度2.4米。
1855-1959年东北部海域15米等深线附近及其以浅海域为淤积;15〜20米海域是冲刷;20米以深海域基本上是淤积,仅局部有冲刷。甜水沟以南海区1959年10米等深线以浅范围内淤积,以深海区则冲刷。淄脉沟口外1959年5米等深线以深海域仍是冲刷。
(三)1959-1984年是以渔洼为顶点的三角洲持续淤进阶段。淤进最迅速的是刁口河海域和清水沟海域。1984年的海岸线接近1855年的15米等深线,在干出线以内区域普遍淤厚11-14米,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淤厚8〜12米,1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淤厚4〜8米,1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淤厚2〜5米。现行河口东北部20米等深线附近冲刷。20米等深线以外又有淤积,厚1~3米。以往迅速淤进的神仙沟五号桩海域,除1973〜1974年因刁口河流路入海口门摆动到神仙沟受影响外,累计停水18年,淤进速度较慢,1984年的5〜15米等深线相应超过1959年的各等深线。埕东、桩西、五号桩、长堤、孤东、一棵树、红柳等油田系此阶段淤出的陆地。湾湾沟区域已半个世纪不受泥沙直接影响,海岸线附近明显蚀退,1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略有冲淤,基本稳定。宋春荣沟以南近30年没有受泥沙直接影响,海岸线至10米等深线略有冲淤,变化不大。
综上所述,1855年以来近代海岸线受自然夷平规律的控制,基本上沿顺直趋势发展。表4—6以1855年海岸线为起点罗列了神仙沟口、湾湾沟附近、永丰河口以南不同深度的淤进距离和速率。由于海岸线淤进中又表现以淤 (进)为主、冲(退)淤(进)交替的过程,表4-7罗列了潮滩外冲淤变化的情况。
1855〜1984年黄河口不同深度淤进表 表4—6
1855〜1984年黄河口海域冲淤量统计表 表4一7
三、海岸延伸特征
(一)叶瓣进积模式:黄河以高含沙量著称于世,高速沉积和频繁决溢导致尾闾河段经常摆动,流路多变。对照流路变迁年序,每次流路变迁均在河口留下一片状如叶瓣的泥沙堆积体。这是由于每条流路改道之初先沿着三角洲凹岸入海。将凹湾填平之后,又向海域淤进凸出。后期发生自下而上的出汊摆动时,又将泥沙向左右两岸扩散堆积,使叶瓣体进一步扩大。经过10多年的淤积延伸,新的叶瓣总是超过旧的叶瓣。如此循环往复,叶瓣之间相互套迭,使三角洲地面抬高,海岸线普遍推进,渐次外延。
(二)拦门沙坝:挟沙水流到河口与潮流引起的底沙再悬浮相遇,形成一个高含沙区(亦称最大浑浊带),在两水交汇、势能锐减和化学因素的作用下,高含沙区内的泥沙大量沉淀,堆积成一道顺河长7公里左右的拦门沙,横亘在口门潮流段内。其纵剖面形态表现为背坡(向河)较缓,前坡(向海)较陡(1983年9月拦门沙前坡比降达8.7‰)。靠近陡坡的拦门坎宽1〜2公里,坎顶水深随潮汐变化不定,低潮时近乎裸露。随着泥沙不断堆积,拦门沙每年向前推进约1.8〜3.5公里。1984年山东省海岸带调查时先后在5月和7月两次实测,拦门沙顺河长4公里,起点距清7断面14公里(参见图4—3),坎顶平均高程﹣0.5米(黄海基面,下同)。1987年9月实测拦门沙长度5.5公里,起点距清7断面17公里,坎顶高程一0.1米。两次测量间拦门沙前沿向前推进4.5公里,平均每年推进1.32公里。
河口拦门沙使入海流路常处半堵塞状态,阻碍泄水排沙。枯水季节不断沉积淤高,洪水季节造成滞流壅水。引发出汊摆动后,又在新口门处堆积新拦门沙。清水沟行水近13年,口门变动较大的13次(参见表4—1)。在拦门沙垂向淤积和横向摆动过程中,海岸线逐步外延,导致侵蚀基面升高,是河口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河口沙嘴发育:其基本过程表现为:初期(游荡散乱阶段)纵向与横向扩展均相对突出;中期(单一深槽阶段)很少漫滩淤积,泥沙主要呈纵向向海延伸;后期(出汊摆动阶段)类似初期状态。据水文资料计算,一条流路的沙嘴延伸速率多年平均为2.3-3.3公里/年。刁口河流路初期沙嘴延伸速率3.18公里/年;游荡阶段为1.85公里/年;归股单一阶段为1.33公里/年;出汊摆动阶段复又增大到1.9公里/年。清水沟流路的沙嘴在1983年9月已突出平均岸线16公里,河长延伸速度达3.55公里/年。当河口沙嘴突出到原海岸线以外时,在水流、风浪、潮流的强烈作用下虽能将30〜40%的泥沙输往深海,余沙仍以原沙嘴为基础继续向前方和两侧漫延堆积。随着诸流路的纵向延长和横向摆动,沙嘴交互套叠,把海岸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
黄河口拦门沙淤进情况图 图4-3
(四)岸线蚀退:黄河口是陆相沉积的淤泥质海岸。当流路发生变迁后,断流的岸段失去陆源物质补给,在海洋动力作用下发生蚀退。据黄世光、王志豪等计算统计:1855〜1984年黄河口共造陆2770.4平方公里,同期蚀退240平方公里,占造陆面积的8.66%。黄委会水科所、济南水文总站等单位刊布资料:1954〜1975年间,河口在80公里范围内淤积造陆786平方公里,同期蚀退面积208平方公里,占造陆面积的26.5%。由于各岸段行河时间长短不同,淤进蚀退亦不尽相同。套尔河口至挑河和宋春荣沟至淄脉沟岸段由于多年不走河,属于相对稳定岸段。挑河至宋春荣沟岸段,半个多世纪以来都在行河,岸线虽然有进有退,仍以淤进为主。刚开始行河和停止走河的岸段淤进和蚀退都很明显。1960年8月由神仙沟改道汉河后,至1963年新河口附近造陆124平方公里,老河口附近蚀退56平方公里,占造陆面积的45%;1964年初由汊河改道刁口河,至1975年新河口造陆500平方公里,老河口蚀退166平方公里,占同期造陆面积的33%(参见表4—5)。
(五)河口沙嘴延伸和海岸线相继全面推进,对上游河道冲淤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但有很大不同。沙嘴延伸引起的河段增长使河道产生溯源淤积的时段短,范围小;河口摆动后引起沙嘴变动又使河段缩短而引起溯源冲刷,亦是时段短、范围小。两者影响上界都在泺口以下。在此范围内,河口口门频繁变化使河段呈间歇性增长或缩短,河床纵剖面也呈间歇性升高或下降。三角洲岸线普遍外延引起的河段增长不但使河口河床抬高,水位上升,而且也向上传播,影响范围超过泺口。王恺忱、周志德在《黄河河口演变规律及其对下游河道影响》一文中指岀:1950〜1975年间,夹河滩和高村以下河段3000立方米每秒的年均水位升高2.07〜2.38米;艾山以下河段在1954-1975年间累计普遍升高2.10米;与同时段河口延伸引起的水位升高值2.13米相一致,近乎平行升高。花园口至利津河段比降30余年来呈变缓趋势等情况,亦证明黄河下游是属于溯源淤积性质,认为产生淤积的主要原因与河口延伸引起的基准面相对升高有关。
河口演变对上游河道的影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黄河三角洲岸线各段变化差异很大,不是普遍向海内均匀淤进。1954年至今,河长尚未达到稳定延长,河道还远未达到平衡状态,仍处于强烈堆积状态。淤积原因主要与来水来
黄河河口工程分布图
沙条件有关,还是自上而下的沿程淤积。河口淤积延伸也受到河口改道引起的溯源冲刷制约,但产生溯源淤积向上游的影响范围有限。从1973-1983年铁谢至一号坝各站水位升降情况(参见表4—8)还看不到由于河口淤积延伸引起下游河道平行淤高的现象。
1973〜1983年黄河下游各断面3000立方米/秒水位升降表 表4—8
注:“一”号表示水位下降值。
总之,近代河口海岸线沿着强烈淤积→强烈蚀退→中度蚀退→轻微蚀退 →相对稳定的格局演变。纵向是上冲下淤,平面上是此冲彼淤,有进有退,进退交替,进的范围小而速率大,退的范围大而速率小。
第三节三角洲演变
一、三角洲沿革
黄河三角洲是以巨量泥沙堆积在入海口附近而形成的扇面状陆地。对其扇面范围和顶点位置有不同解释。史前时期的黄河下游即以河南省孟津为顶点,在北至天津大沽口、南至淮河入海处的广袤地带纵横奔流,迁徙无定,波及冀、鲁、豫、皖、苏五省20多万平方公里。因多次改道迁徙和频繁决溢沉积塑造的广大地区,称古代三角洲。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又塑造岀一个小范围的三角洲,即“利津县城以东黄河口部分地区。”①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利津宁海(今垦利)为顶点,北起套尔河口、南至淄脉沟(南旺河)口的扇状地带称近代黄河三角洲,至1984年面积已逾6000平方公里(参见表4—9)。
黄河三角洲各类土地面积表 表4一9
建国后,河口地区经济开发逐步加快。在人为控制下将河道摆动顶点移至垦利渔洼(左岸利津四段村)附近,北至挑河,南至宋春荣沟之间的三角洲扇形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称现代黄河三角洲(见图4—4)。
二、洲面淤积特征
据利津水文站1949-1988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输至河口地区的泥沙年均10.03亿吨。进入河口地区的泥沙有24%左右沉积在大沽零米线(陆地)以上,有40%左右沉积在零米线以下的滨海区,其余被海流输至深海。刁口河流路行水12.5年,来沙总量135.2亿吨。其中的21.6%沉积在陆上抬高洲面,44.1%延伸沙嘴填海造陆,34.3%被输往深海。在尾闾流路频繁变迁的过程中,以自上而下、左右交替的形式,平均每年填海造陆3〜4万亩的速度,形成由若干大小沙嘴和海湾联接、外沿曲折、突向东北的扇状陆地。黄河自1855〜1955年在近代三角洲扇面上发生过50多次决口或改道,洪流四溢,非冲即淤。为避水患而修筑的堤埝纵横交错,围堵拦截,形成岗坡沟洼相间的复杂地形和起伏涟漪的微地貌。故道地形相对较高,故道相距较远者,其间多为洼地。故道相距较近,走河时间较长而又无堤防者,高地连成一片。三角洲中部行河时间较长,地面相对较高,呈现中间隆起的拱形曲面。
沉积在洲面上的泥沙,大致分为沙壤土和粘土。故道主流处地表均露沙土,故道两侧滩地多为沙壤粘土互层,河间洼地逐渐过渡为较厚的粘土层。
河口相对稳定海域条件变化不大时,泥沙颗粒粗细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在横向上,河口沙嘴部位颗粒较粗,两侧较细;在纵向上,陆地和滨海区前沿顶部较粗,愈向外海愈细。利津水文站多年测验成果(参见表4—10),输至河口地区的泥沙多为悬移质中的冲泻质,年均中数粒径d50在0.0064〜0.038毫米之间,其中d50<0.025毫米的泥沙,占总量的50%强;d50<0.010毫米的极细沙占总量的25%。因大部分细沙易被海流挟入深海,沉落在三角洲岸坡(包括水下部分)上的泥沙颗粒相对粗化。对浅海底质资料分析表明,三角洲岸波上的泥沙分布亦有分选现象。通流海域5米等深线以内d50>0.03毫米,10米等深线以外d50<0.02毫米,且有很大范围d50<0.01毫米,是径流泥沙的扩散区域。不通流海域泥沙分布为上部粗,下部细,但都是d50>0.03毫米。
每条流路的泥沙沉淀表现为陆上粗沙比例大,细沙比例小;水下则相反。刁口河流路的粗颗粒泥沙中70%淤积在陆上沙嘴顶部,仅有7.5%能被输送到海岸线坡脚以外。细颗粒泥沙中72.4%被输送到沙嘴前沿以外。流路发育
利津贴(刘家夹河)逐年水沙特征值统计表 表4-10
(续表)
(续表)
的各个阶段,泥沙分布也不同。改道初期,几乎全部来沙都淤积在滨海区时,水上部分细沙比例相对较大;当沙嘴逐渐稳定和外突时,细颗粒泥沙的绝大部分被输至深海,陆上存留比例甚少。还有一部分滞流在沙嘴两侧的凹湾处,形成以极细物质为主的浮泥区,范围约几平方公里,浮泥厚1〜5米不等,渔民称 “烂泥湾”,是良好的避风场所。
另据水文部门测验证明,由于黄河有水沙异源的情况,在不同时段和地区的水沙组合对河口泥沙沉积有很大影响。年度之内,汛期悬移质组成一般较细,非汛期较粗。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来沙与龙门至三门峡区间来沙,粗细程度亦有差异。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与改建前后比较,来沙粗化明显。据1950〜1975年资料统计,三门峡水库建成前(1955〜1959年),粒径小于0.025毫米的泥沙占总量的64.2%;水库建成运用后(1960〜1965年)占55%;水库改建期间(1967〜1973年)占44.9%;水库恢复正常运用(全年控制)后(1974〜1977年)占45.8%。清水沟流路行水后,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改变为“蓄清排浑”,泥沙颗粒大于0.025毫米的床沙质含量占总量的61.5%。
三、三角洲开发
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古三角洲边缘已建置永利镇等较大聚落,定居之民分布在陆地或沿海一带从事农桑或捕捞。随着人口繁衍生息,数量增加和经济发展,至金明昌三年(1193年)十二月永利镇升为利津县置,成为三角洲边缘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之一。其后,三角洲腹地成为大清河入海流经之地,水流清澈,河槽深邃,利津城南土地相继脱盐变为宜耕区,农桑发展加快。城北土地靠近滨海,含卤重,不宜农作,却促发盐业、渔业和海关运输业及商业的兴起,先后形成丰国(今汀河)、永阜、宁海等较大村镇,出现“巨海枕其北,清河绕其东,南有桑枣之饶,西通舟车之利”①的繁华昌盛情景。
明代初期,山西洪洞及直隶枣强等地大量移民迁至三角洲定居,垦植面积迅速增加。至清代中叶,三角洲顶部的农业和滨海处盐业、浅海区渔业、铁门关及城镇商业、水陆交通业等都相当发达。“昔济水由利津入海,名曰大清河,河门通畅,南北商船由渤海驶入河口在铁门关卸载,由河内帆船输运而上。彼时物品云集,商人辐凑,此为商业最盛时期”。①永阜、丰国、富国等地成为山东省大型盐场。清康熙年间奖励生育,人丁剧增,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利津县册报人口已达4.78万余户,近27万人,拥有土地45万余亩。仅永阜盐场即有滩池420付,产盐为8场之冠。除在鲁西北销售外,还远销河南、江苏等地。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初时沿河堤防断断续续,东明、荷泽一带时常泛滥成灾,滞洪留沙,近海地区水害尚不严重。至清光绪九年(1883年)利津以上堤防完整,河口地区水患加重,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先后造成大清河航道淤塞,铁门关码头废弃,各大盐场被毁。繁华数百年的近海地区经济逐渐萧条。但在不景之中,黄河却以独特的水沙在新老套迭的河道上轮回变迁,淤海造陆,再度使三角洲面积大幅度扩展。清光绪末年,宁海以上堤防亦具相当御水能力,决溢较少,农业已见复兴。宁海以下新淤陆地上,灶户盐民开始改营农作。民国初期,政府鼓励垦荒,邻县穷苦农民先后进入三角洲内拓地垦荒,仅凭县府颁发的领单验单即可尽力粗放耕耘,每亩收费甚微,使三角洲近海地区农业初见生机。民国15年(1930年),韩复榘部五十九旅进洲屯垦;民国24年(1935年),鲁西南灾民4200余人由政府组织迁居河口择地栖息,进一步加速了近海地区农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黄河三角洲成为清河区、渤海区革命根据地。民国30年 (1941年)中共渤海区委设置垦区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民国32年(1943年)建置垦利县人民政府,使三角洲再度出现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繁荣阶段。民国31年(1942年)至34年(1945年)间,由人民政府安置在垦利县的移民近2万户,约11万人,垦植土地近45万亩。盛产的谷物、豆类、棉花、油脂、酱菜等农副土特产品,不但保障解放区人民的物质需要,亦成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
建国后,在兴修水利设施、改革耕作习惯、推广科学种植、引进机械电力的基础上,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林、牧、副、渔等业。1949年后,又组织四次向三角洲迁民,至1960年,利津、垦利两县共安置移民5万余人。自1950年起,相继组建广北、五一、黄河、渤海、海滨、联合、共青团、同兴、淄脉沟、青坨等中小型国营农垦、劳改场,济南军区军马场及一千二(渤海)、孤岛等林场。1961年始,至1986年底,在潮河至永丰河约5000平方公里内相继探明油田23处,地质储量可观,年生产能力近1500万吨。以石油化工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开始萌发壮大,带动其他行业竞相起步,使三角洲面貌焕然一新。
1983年东营市建制后,制定“油洲加绿洲”的战略开发规划,以能源化工和农林牧渔盐业综合发展为目标,使黄河三角洲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和商品粮生产基地。现代工业、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交通运输、商业供销、文教科技、农田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亦初具规模。三角洲经济进入全面振兴、综合开发的新时期(参见图4—4)。
历史上,黄河三角洲曾经保持丛林密布、草木繁茂的自然生态环境,植被覆盖面积达60%以上,1953年仍达20.93%。60年代以来,毁林开荒、滥垦酷牧,至1981年植被覆盖面积仅有2.93%。经有关部门和人士疾呼,引起各级政府重视,遂提倡植树造林,播种草场,绿化状况已见转机。至1987年底,植被覆盖回升到近60万亩,约占三角洲面积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