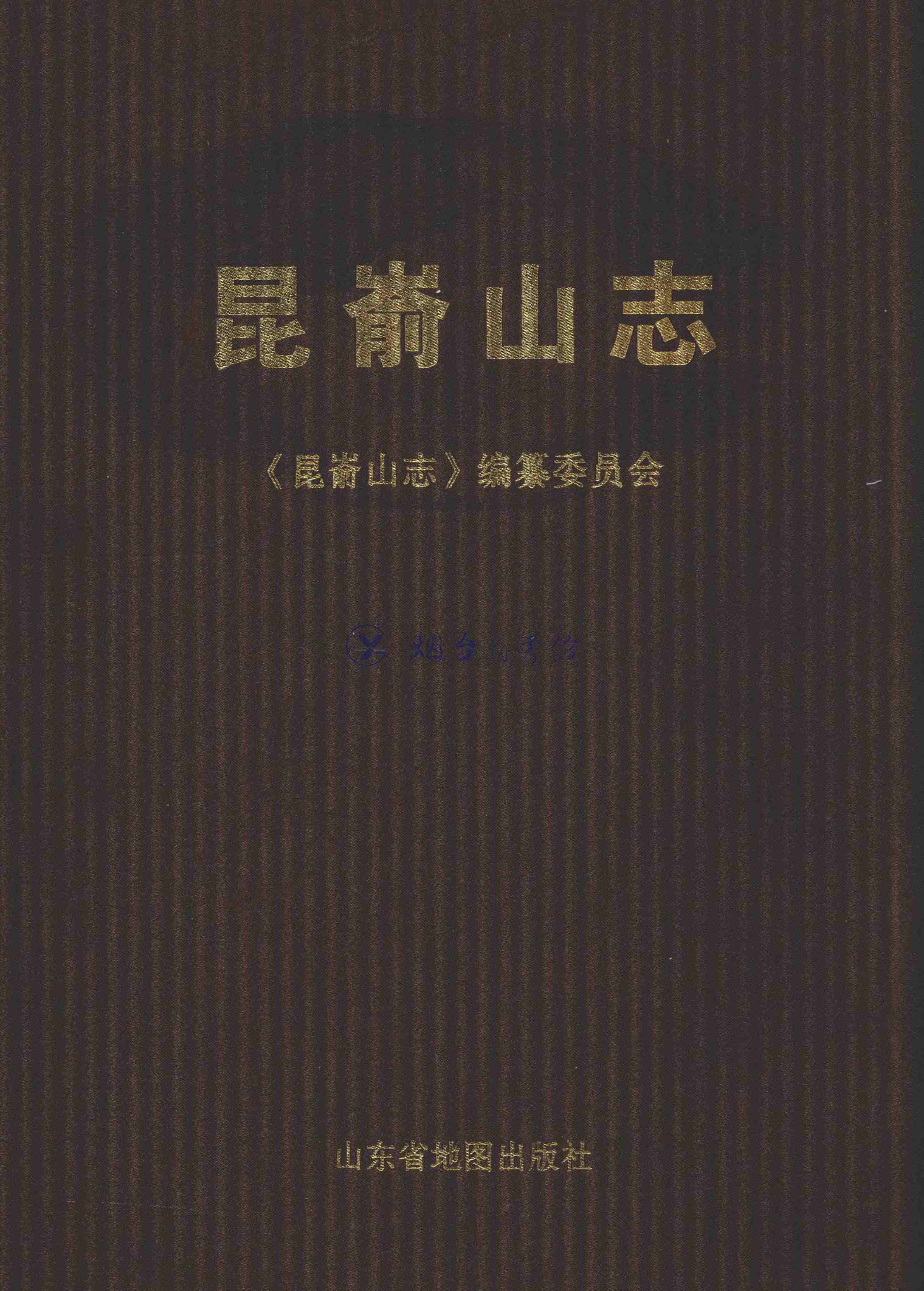内容
法静俗名周培明,1917年出生于牟平区莒格庄镇椁椤村村西金斗夼,又称西庵。其祖父是文登高村河西村人,后来经文登的二马、厥上、集后、葛家、汪疃等地五次辗转,才来到西庵。弟兄姊妹七人,三男四女,培明排行老四。12~16岁,到本村小学读4年书。
下学就帮家里干农活。那时家有13亩地,9口人,一头小毛驴。当时粮食产量很低,一亩小麦能打110斤就是好年景,产量最高的是地瓜,所以,最常吃的饭就是地瓜干。即便是地瓜干,也不够吃,挨饿是经常的事。
附近贵家庄有个60多岁的姜诚义,常到西庵闺女家住。1937年秋,他看周挨饿受冻的样子,非常可怜,就介绍他到神清观当道士,说那里有饭吃,还能学识字。周心里十分高兴。第二天午饭后,周瞒着父母,由姜诚义领着,去了神清观,见到宫道长。宫道长己70多岁,身材不高,瘦瘦的,身著一身鸟蓝色的道袍,神情平和而慈祥,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他仔细地打量着问周说:“出家当道士,你自己愿意吗?”周急忙对他点点头说:“愿意。”他看周回答的挺坚决,就叮嘱道:“那好,到观罩可要守规矩呀!”然后他又转过头来对姜说“这孩子我看挺好,与道有缘。等吃过晚饭,咱们再到大殿里正式拜师。”
晚饭是简单的,只有一个菜,吃的是黑馒头(面里带麸),这是周培明入道出家的第‘顿饭。当天晚上,在神清观的大殿内举行出家拜师仪式。师父宫嗣海道长立在大殿正中的老君像前,姜诚义作为证人立在旁边。首先给太上老君上了三支檀香,接着又跪在蒲团上对着师父叩了三个头,然后师父对周讲出家人应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规矩,简单的拜师仪式就算结束了。虽然整个仪式很简单,但至今周培明仍然能回忆起师父那和缓但透着坚定的声音:“第一要尊师重道,第二要守三皈五戒。”师父详细给他讲三皈五戒的内容。三皈指的是:皈依仙、皈依仙法、皈依道士。“仙”指的是大智大慧的人;“仙法”指的是仙讲的教义;“道士”是指信奉和宣扬教义的人。五戒指的是戒杀、盗、淫、妄、酒。应该说这些规矩和当时佛家的戒律基本上是一样的。讲完这些后,师父很郑重地加上一句:“不守规矩,逐出山门。”声音不大,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至今周还音犹在耳。
由于神清观一直属全真教龙门派的,所以出家后,刘慧仙师爷便按照龙门派百字年谱中“崇高嗣法兴”的顺序给周取道号“法静”。这样,周就正式成为神清观龙门派第29代弟子,当时20岁。
龙门正宗百字谱:
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
至立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维懋,希夷衍自临。
微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玅中黄贵,圣体全用功。
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
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
拜过师父后,宫道长又送周一身道装,包括乌蓝色的道袍、白色高腰袜、布鞋等,从此按道士的要求开始蓄发。
大约三、四天后,父母来观上看他,看他能吃上饭,道长和居士们待他都挺和善,也就放心了。
当时神清观除了师父和法静之外还有葛世二、孙长为两个人,都不是出家人。葛世二是闯关东回乡的孤寡老头,神清观收留了他;孙长为是在神清观养病的人,他的家人经常来看他。都是昆嵛山附近的人。
当时的神清观是明末第三次毁于战火后,在清朝初期建造的。后来又经过几次修缮,整个建筑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中间的大殿(老君殿)共三间,房间很宽敞,大殿由四根支柱支撑着整个屋架房梁。迎门是太上老君的泥塑彩绘像,两旁有泥塑童子抱手侍立,整个大殿威仪肃穆、宝相庄严。大殿东西两边墙上,是遮住整个墙壁的高高的黄色经橱,橱架上摆满用黄绸缎包裹的书籍。后来才知道,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皇帝颁发了一道诏书,赐给昆嵛山道众《道藏经》一部,神清观和玉虚观各半部。
大殿西边真武殿里正中是真武大帝的坐像,泥塑彩绘贴金脸,坐像前摆放着云纹底座的木制牌位,上写:北极玄天真武大帝。大殿东面七真殿的王重阳及弟子的塑像也塑得很好,有特色。
当时神清观院内的石碑非常多,都是神清观历史的见证,但好多碑刻现在看不见了。他印象最深的是“铜碑”,丘祖的《青天歌》碑和《十六绝诗》碑,以及宫卜万的《烟霞洞听子规歌》碑。
神清观东侧的小山岭叫清风岭,有卧龙坪,有唐四仙姑石龛和清风亭。唐四仙姑的石龛听说现在还有一些残石在。
师父对法静要求很严,他是一家之长,很有涵养。他批评人时从不发火,就是几句话,甚至几个字,顶多口气稍微严厉一点。比如当他见到山下有些到神清观游玩的人,不懂规矩,不尊重出家人的信仰,乱说乱道,让他感到很不舒服而又无法劝说时,他就会念叨“孽障”二字,来排遣他的无奈和不满,这是他表达严厉指责时的口头语。
神清观的道士留发但不加冠,头发一般是每七天一洗,自己烧水,用肥皂洗。鞋子是普通的圆口手工纳底布鞋,衬衣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外面罩一件灰色长袍,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衣服都是自己动手浆洗,不假他人。衣服穿出破洞后就随手找一块布缝上,布的颜色没有特别的规定,只要干净不是红布就行。所以时间长了,衣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百衲衣”。师父当时就常年穿着这样的一件百衲衣,由于经年累月的一层层叠补,衣服最厚处起码有半指那么厚。这并不是买不起一身衣服,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尊重神清观几百年来所传下的道统,体现出家人以修道为唯一目的,苦己勤俭,不以奢华为尚的精神,同时也为后学作出榜样。另外,作为一个修道者,只有破除“我相”,方可在修行的路上继续向上进阶,对未得道的人来说,苦行就是破除“我相”的一种修行方法。
师父把观上的规矩一样样地教给法静,比如说:出家人进出道观门时一定要先迈左脚,对人打招呼行抱拳礼时,也是左手抱右手,两手打拱,鞠躬揖下。
神清观属十方庙,有义务接待远道而来的出家人,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都一律平等相待,有度牒的要查看度牒,没有度牒的同门要考宗谱,能背诵下来的便确定是同门,相处时便显得亲热一些,交流的话也多一些。但无论真假都留宿招待。
当年的神清观名义上有三位老道长,一位就是周的师爷孙高起,已经80多岁,第二位是他的师弟刘慧仙,兼神清观东南庄头庙的道长,很少回神清观,后来也还俗了。法静师父宫嗣海,是玉林店镇西柳庄人,是孙高起的徒弟。由于孙高起兼任岳姑殿下坡里庙的道长,也不常到庙里来,所以师父宫嗣海实际已经接管了观里的一切事务,成为事实上的当家人。孙师爷在法静出家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两年中也就见了他两三次。去世时法静去戴过孝,他也葬在神清观下的道士茔地里。
神清观的道产是十来亩地和一定范围的山林。这十来亩地大都十分贫瘠,只能栽植地瓜。所以,一年里的主要食物是地瓜干。玉米和小麦则是用地瓜干到集市上换来的。这十来亩地,大部分由下面村里的百姓租种,每年交给我们一定量的地瓜干。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上山打柴外卖,用来补贴观里的日常费用。所拥有的山岚,就是神清观南北两山山脊之间的部分。
观里平常饮食比较单一,每餐有咸菜,一个大菜,大多是熬白菜和萝卜。仍然坚持吃素,持不杀戒,不但不吃肉,就连做菜时用的油,也只用花生油和豆油。因为油坊离周老家很近,所以每次买花生油时,法静都能顺路回家看看父母,除此之外,没有单独回过家。
周这一生都坚持吃素,即便还俗了也绝少吃肉,自己也确实体会到吃素的好处。不说别的,吃不吃素,人体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就不一样,长年吃素的人,呼吸和散发出来的气味清,吃荤的则带有一种难闻的浊气。
道观里是不过俗家节日的。神清观一年中主要的节日有:二月十五太上老君圣诞日;四月十五天官节;七月十五地官节;十月十五水官节。过节时,能改善一下生活,吃一顿馒头。除此之外就是早晚两次到大殿上香和念早晚功课经(平日只有晚功课),晚上要敲钟,一共九九八十一下,每九下一停顿,钟声传得很远,十里之内都听得清清楚楚。大钟放在大殿门东的一个木架上,是生铁铸成的,听师父说是很早以前从苍山南的廖观(公)庵搬过来的。
神清观上香用檀香,一天三次,一次三根,这是神清观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檀香是宫道长专门从烟台的药材行买回来的檀香木;周来了以后,这个活就交给周。周记得买一块直径3寸、高2寸左右的檀香木需要北海币十多万元。刚买回来的檀香木是一整块圆木,要把它一块块地劈开,劈成像火柴棍那么长短和粗细,叫“寸香”。尽管道观的经济拮据,但上香从来不马虎,保质保量。
神清观虽然只有法静和师父两个出家人,但在学习道家经典方面丝毫不马虎,每天吃完晚饭就把桌子放在炕上,师父和法静坐桌子两旁,师父教徒弟学习,每天两小时左右,天天如此,雷打不动。虽然周出家前读过几年书,但拿起道家的经典仍然有很多字不识,念不上句,所以开始时,师父就先从教学经典识字起步。观里有一本《康熙字典》,不会的字就让徒弟查。学的第一本经典是《太上说常感应篇》,就是现在的《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对周的人生观和影响最大,至今仍然能够背下来。所念的经是早、晚功课经合在一起的。其中《早功课经》的经文是大道洞玄虚,有念无不欺;炼质入仙真,随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无苦解;习归太上经,净念稽首礼。《晚功课经》是:重重无名是苦根,苦根除尽善根存。但凭慧剑威神力,跳出轮回无苦门。道以无心独有情,一切方便是修真。若归圣智源通理,便是升天得道人。
师父给徒弟讲解了经文的含义以后,就不在炕上学了,一定要到大殿老君像前敲着木鱼吟诵。师父恪守古制,每天在晚功课中唱诵这些经文。唱诵时师父左手敲木鱼,右手击鼓,按照固定的节奏和曲调进行,整个过程节奏舒缓、曲调和雅。周以后在学习其它的经典时,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下来。
周出家半年以后,师父开始系统地教授他学习道家经典,所用的课本就是神清观里的《道大藏经》。这时的教学地点也在大殿里。历代祖师们精心保护这套经书,使用的时候怕用手翻污损书籍,都是用竹签页一页翻的。《道大藏经》虽然经历了几百年,仍然没有大的损坏。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容易,既要经常使用,还要精心保护。
关于静坐的要领,师父是这样讲的:“仰面起邪火,低头阴水生,腰弓不通气,闭目阳不升。”即静坐时两眼不可闭紧,因为两眼闭紧了,容易发生很多弊病,出现很多阴境,所以二目要呈垂帘状。这些东西现在都公开了,很多书上讲的也很详细,但很多人做的并不对,主要原因是没有老师现场指导。
有人问周还有没有深入往上的功法,周老实地告诉大家,没有。当年师父教的就是这些。周一生就是靠着这点看着不起眼的东西,几次跳过鬼门关,活到今天。周认为现在的人好高骛远,不肯在最简单的地方下功夫,其实最初的就是最后的。周不否认可能有更深一层的功法,但没有清净戒律作基础只能学出一身毛病,起码不会长寿。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在圆寂时,弟子问他走后世人如何修行,他回答“以戒为师”。真正的佛教、道教的修行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当初师父到处找有心出家的小道士,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找一个做饭的伺候自己。师父直到临终的前一天还能够行动自如,能够自己照看自己。他找徒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昆嵛山道医的这门手艺传下去。因此师父在教周学习时督促甚严,他担心有生之年不能把龙门派医术传下去,对不起历代祖师。
也许师父已经预感到未来时局的艰难,有一次闲聊肘,他看似无意地对徒弟说:“将来的时局要有大的变化,观里恐怕呆不长久了,我教你学道医吧,一来你自己以后可以有个吃饭的本事,另外这也是咱神清观龙门派一脉独传的道门医术。”听说师父要教医术,周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师父很郑重地告诉周说,昆嵛山龙门派道医传到他这里是第四代,希望徒弟好好认真学习,不要怕吃苦,将来机缘合适时,要发扬光大这一道门医术,为民造福,一定不要让它失传。
周培明的道医技艺是宫师父手把手,一对一教出来的,是师父的亲传。
周培明出家的第一年,白天主要以学习做饭、打扫清洁、晚上学识字为主。当有了识字的基础后,第二年就开始在师父的指导下,学习道医的第一部经典《伤寒论》,第三年开始学习《金匮要略》,第四年学习《温病条辨》,第五年学习《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一书是穿插在中间,结合着上山采药学的。
周培明就是在学完了《温病条辨》以后开始独立行医的。在这之前几年,他一直都是跟随师父,边干边学。开始只是帮助抄写药方、配制草药等。抄写药方是中医师父带徒弟的主要方法,是师父言传身教的主要手段。由于平日经常有人慕名到观里请老道长看病,所以周很快地就学会把脉、舌诊、配方剂等技术。到后来,有了病号,师父就常常先让徒弟看,看完了他再给审查一遍,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他就纠正过来,待病人走后,重新给徒弟仔细分析、讲解错在何处,应如何正确诊治,并及时传授道医诊疗的相关要领、诀法等窍门。周的医术进步很快,也慢慢得到师父的认可。
师父还传给他一本老的《汤头歌诀》书,那书看样子能有一百多年,书里的纸张都已经发黄了,里面收录340多个药方。后来周又往里添加100多个,共计有400多个方子。2000年前后,有个烟台人向他借阅。后来她说不小心给弄丢了,还了周一个复印本。其实方子是死的,怎么辩证活用才是精髓。
神清观道医传下来很多的方剂剂型,到周来神清观时,很多的剂型已经无力制作了,只能尽能力制做一些相对简单的。但那些方子的配伍周都记了下来。
道医治病的一个特点是需要病人对生活有正确的态度,但很少有人把生活态度当成一个治病的方法。一个人没有了烦恼,心平气和了,身体的能量才会积聚、运行起来,去修复体内受损的部分。还有一点很重要,道教中人对疾病讲究的是预防,并不是治疗,强调“治未病”。因为预防是一种积极而主动的行为,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而治疗则显得被动,况且有些病也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道家养生讲究“治未病”,也就是防忠于未然。一个修道的人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你入门修炼的就是对自身及外界的这份敏感,道教的根本理论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法则,这个法则用于人身就是养生和预防疾病。丘祖的《摄生消息论》就是专门讲这方面内容的,其中按四季对应脏腑的不同分为春夏秋冬摄生消息,内容具体而丰富。
学道医难啊!道医与普通中医在医理上、治疗的方子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在修持上,道医学最核心的东西叫内证学,有守一、守窍、守呼吸等许多方法。在这一点上周认为自己只是有一点小体会,所证有限。
到山里采药,是周和师父每年必干的一件事。采药首先要认药,要知道每一种药材长的什么模样,在哪里有分布,认识它的生长环境。不同的药,喜性不同,有喜干燥的,有喜潮湿的,有生长在前阳的,有生活在背阴的,有喜湿气接近水的等等,都要清楚。
中药材有几千种,昆嵛山道门常用药材也就两三百种。药材的合理采集不仅可以保证药材的质量、药效,而且对保护、扩大药源也很重要。周认识中草药都是师父亲临现场言传身教,所以周对各种药材的分布地点、寻找方法以及药性的特点、采集的时间、炮制的方法等等都了然于心,特别是对一些珍稀药材的寻找,尤为熟知。如今在昆嵛山里还坚持采药的几位老人,当初都跟周学过。
按昆嵛山龙门派道医历代传下来的规矩,师徒所采的草药从来不外卖,全部用来给病人治病,从不收钱。就是到外面去买来的药,用于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也是一分钱不收。
师父是1943年6月间去世的。在去世前的十多天自身就有了感觉,不能再上山了,周也感觉到他的体力明显下降。一天早晨,师父把周叫过来,作最后的叮嘱,然后自己到房间里休息了,到中午时就去世了。当时他的身体呈吉祥卧姿态,安详地躺在那里。在整理好师父的遗容后,周就下山找来几个熟人帮忙,把师父放进棺木里,抬到山下神清观历代道士的公墓,按照辈分次序,把师父安葬了。
师父羽化后两个月,周便按照师父的嘱托,找到当时牟平城里“天春堂”(西门里)药铺的老板,去学习认识昆嵛山以外的中草药。师父在去世前曾对周说过,光靠昆嵛山的中草药治病是不够的,还要认识其它的中草药才行。“天春堂”的老板和师父是老关系,有时他也跟师父请教一些治病的方法。周在“天春堂”一共呆了大约七个月,期间也偶尔回到观上住,还发生了被三次动员还俗的事情。
到1944年秋天,周最后一次返回神清观,带上观里剩下的一些中草药和八宝坤顺丹、益母膏等成药,来到玉林店镇的大屯圈村,开始自己开药铺谋生。此后,神清观就荒废了。这期间,经人介绍,他和徐士文结为夫妻。她小周六岁,是给她父亲治病时认识的。结婚后,在老家椁椤村的西庵上安家,育有四女二男。一直到1994年才从庵上搬进村来。老伴于2006年冬去世,时年86岁。
1947年,周被动员参加支前的民工队伍,负责救治伤员。当年11月复员继续开药铺,后到昆阳区药社(就是后来的莒格庄医院),以后又参加合作医疗。1958年县卫生局调周到省中医学院进修一年。1959年学习回来后,被分配到威海温泉疗养院(山东省总工会所属)任保健医生。1965年开始,县卫生局调周参加乡村五期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周尽力把学的东西传给他们。1976年,周又被返聘到水道医院,帮助教学一年,后来又到莒格庄医院坐堂四年。辞了在医院的工作,在家里给老百姓免费看病、开处方,让病人自己拿着周的方子到药铺抓药,给患者节省了大笔治疗费用。
周现在91周岁了,还在不停地学习,看病、开方子。每当想起这一辈子能有机会帮助这么多人,和这么多人结缘,心里总是乐滋滋的。(选自刘学雷著《昆嵛道医——神清观末代道士访问记》)
下学就帮家里干农活。那时家有13亩地,9口人,一头小毛驴。当时粮食产量很低,一亩小麦能打110斤就是好年景,产量最高的是地瓜,所以,最常吃的饭就是地瓜干。即便是地瓜干,也不够吃,挨饿是经常的事。
附近贵家庄有个60多岁的姜诚义,常到西庵闺女家住。1937年秋,他看周挨饿受冻的样子,非常可怜,就介绍他到神清观当道士,说那里有饭吃,还能学识字。周心里十分高兴。第二天午饭后,周瞒着父母,由姜诚义领着,去了神清观,见到宫道长。宫道长己70多岁,身材不高,瘦瘦的,身著一身鸟蓝色的道袍,神情平和而慈祥,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他仔细地打量着问周说:“出家当道士,你自己愿意吗?”周急忙对他点点头说:“愿意。”他看周回答的挺坚决,就叮嘱道:“那好,到观罩可要守规矩呀!”然后他又转过头来对姜说“这孩子我看挺好,与道有缘。等吃过晚饭,咱们再到大殿里正式拜师。”
晚饭是简单的,只有一个菜,吃的是黑馒头(面里带麸),这是周培明入道出家的第‘顿饭。当天晚上,在神清观的大殿内举行出家拜师仪式。师父宫嗣海道长立在大殿正中的老君像前,姜诚义作为证人立在旁边。首先给太上老君上了三支檀香,接着又跪在蒲团上对着师父叩了三个头,然后师父对周讲出家人应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规矩,简单的拜师仪式就算结束了。虽然整个仪式很简单,但至今周培明仍然能回忆起师父那和缓但透着坚定的声音:“第一要尊师重道,第二要守三皈五戒。”师父详细给他讲三皈五戒的内容。三皈指的是:皈依仙、皈依仙法、皈依道士。“仙”指的是大智大慧的人;“仙法”指的是仙讲的教义;“道士”是指信奉和宣扬教义的人。五戒指的是戒杀、盗、淫、妄、酒。应该说这些规矩和当时佛家的戒律基本上是一样的。讲完这些后,师父很郑重地加上一句:“不守规矩,逐出山门。”声音不大,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至今周还音犹在耳。
由于神清观一直属全真教龙门派的,所以出家后,刘慧仙师爷便按照龙门派百字年谱中“崇高嗣法兴”的顺序给周取道号“法静”。这样,周就正式成为神清观龙门派第29代弟子,当时20岁。
龙门正宗百字谱:
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
至立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维懋,希夷衍自临。
微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玅中黄贵,圣体全用功。
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
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
拜过师父后,宫道长又送周一身道装,包括乌蓝色的道袍、白色高腰袜、布鞋等,从此按道士的要求开始蓄发。
大约三、四天后,父母来观上看他,看他能吃上饭,道长和居士们待他都挺和善,也就放心了。
当时神清观除了师父和法静之外还有葛世二、孙长为两个人,都不是出家人。葛世二是闯关东回乡的孤寡老头,神清观收留了他;孙长为是在神清观养病的人,他的家人经常来看他。都是昆嵛山附近的人。
当时的神清观是明末第三次毁于战火后,在清朝初期建造的。后来又经过几次修缮,整个建筑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中间的大殿(老君殿)共三间,房间很宽敞,大殿由四根支柱支撑着整个屋架房梁。迎门是太上老君的泥塑彩绘像,两旁有泥塑童子抱手侍立,整个大殿威仪肃穆、宝相庄严。大殿东西两边墙上,是遮住整个墙壁的高高的黄色经橱,橱架上摆满用黄绸缎包裹的书籍。后来才知道,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皇帝颁发了一道诏书,赐给昆嵛山道众《道藏经》一部,神清观和玉虚观各半部。
大殿西边真武殿里正中是真武大帝的坐像,泥塑彩绘贴金脸,坐像前摆放着云纹底座的木制牌位,上写:北极玄天真武大帝。大殿东面七真殿的王重阳及弟子的塑像也塑得很好,有特色。
当时神清观院内的石碑非常多,都是神清观历史的见证,但好多碑刻现在看不见了。他印象最深的是“铜碑”,丘祖的《青天歌》碑和《十六绝诗》碑,以及宫卜万的《烟霞洞听子规歌》碑。
神清观东侧的小山岭叫清风岭,有卧龙坪,有唐四仙姑石龛和清风亭。唐四仙姑的石龛听说现在还有一些残石在。
师父对法静要求很严,他是一家之长,很有涵养。他批评人时从不发火,就是几句话,甚至几个字,顶多口气稍微严厉一点。比如当他见到山下有些到神清观游玩的人,不懂规矩,不尊重出家人的信仰,乱说乱道,让他感到很不舒服而又无法劝说时,他就会念叨“孽障”二字,来排遣他的无奈和不满,这是他表达严厉指责时的口头语。
神清观的道士留发但不加冠,头发一般是每七天一洗,自己烧水,用肥皂洗。鞋子是普通的圆口手工纳底布鞋,衬衣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外面罩一件灰色长袍,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衣服都是自己动手浆洗,不假他人。衣服穿出破洞后就随手找一块布缝上,布的颜色没有特别的规定,只要干净不是红布就行。所以时间长了,衣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百衲衣”。师父当时就常年穿着这样的一件百衲衣,由于经年累月的一层层叠补,衣服最厚处起码有半指那么厚。这并不是买不起一身衣服,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尊重神清观几百年来所传下的道统,体现出家人以修道为唯一目的,苦己勤俭,不以奢华为尚的精神,同时也为后学作出榜样。另外,作为一个修道者,只有破除“我相”,方可在修行的路上继续向上进阶,对未得道的人来说,苦行就是破除“我相”的一种修行方法。
师父把观上的规矩一样样地教给法静,比如说:出家人进出道观门时一定要先迈左脚,对人打招呼行抱拳礼时,也是左手抱右手,两手打拱,鞠躬揖下。
神清观属十方庙,有义务接待远道而来的出家人,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都一律平等相待,有度牒的要查看度牒,没有度牒的同门要考宗谱,能背诵下来的便确定是同门,相处时便显得亲热一些,交流的话也多一些。但无论真假都留宿招待。
当年的神清观名义上有三位老道长,一位就是周的师爷孙高起,已经80多岁,第二位是他的师弟刘慧仙,兼神清观东南庄头庙的道长,很少回神清观,后来也还俗了。法静师父宫嗣海,是玉林店镇西柳庄人,是孙高起的徒弟。由于孙高起兼任岳姑殿下坡里庙的道长,也不常到庙里来,所以师父宫嗣海实际已经接管了观里的一切事务,成为事实上的当家人。孙师爷在法静出家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两年中也就见了他两三次。去世时法静去戴过孝,他也葬在神清观下的道士茔地里。
神清观的道产是十来亩地和一定范围的山林。这十来亩地大都十分贫瘠,只能栽植地瓜。所以,一年里的主要食物是地瓜干。玉米和小麦则是用地瓜干到集市上换来的。这十来亩地,大部分由下面村里的百姓租种,每年交给我们一定量的地瓜干。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上山打柴外卖,用来补贴观里的日常费用。所拥有的山岚,就是神清观南北两山山脊之间的部分。
观里平常饮食比较单一,每餐有咸菜,一个大菜,大多是熬白菜和萝卜。仍然坚持吃素,持不杀戒,不但不吃肉,就连做菜时用的油,也只用花生油和豆油。因为油坊离周老家很近,所以每次买花生油时,法静都能顺路回家看看父母,除此之外,没有单独回过家。
周这一生都坚持吃素,即便还俗了也绝少吃肉,自己也确实体会到吃素的好处。不说别的,吃不吃素,人体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就不一样,长年吃素的人,呼吸和散发出来的气味清,吃荤的则带有一种难闻的浊气。
道观里是不过俗家节日的。神清观一年中主要的节日有:二月十五太上老君圣诞日;四月十五天官节;七月十五地官节;十月十五水官节。过节时,能改善一下生活,吃一顿馒头。除此之外就是早晚两次到大殿上香和念早晚功课经(平日只有晚功课),晚上要敲钟,一共九九八十一下,每九下一停顿,钟声传得很远,十里之内都听得清清楚楚。大钟放在大殿门东的一个木架上,是生铁铸成的,听师父说是很早以前从苍山南的廖观(公)庵搬过来的。
神清观上香用檀香,一天三次,一次三根,这是神清观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檀香是宫道长专门从烟台的药材行买回来的檀香木;周来了以后,这个活就交给周。周记得买一块直径3寸、高2寸左右的檀香木需要北海币十多万元。刚买回来的檀香木是一整块圆木,要把它一块块地劈开,劈成像火柴棍那么长短和粗细,叫“寸香”。尽管道观的经济拮据,但上香从来不马虎,保质保量。
神清观虽然只有法静和师父两个出家人,但在学习道家经典方面丝毫不马虎,每天吃完晚饭就把桌子放在炕上,师父和法静坐桌子两旁,师父教徒弟学习,每天两小时左右,天天如此,雷打不动。虽然周出家前读过几年书,但拿起道家的经典仍然有很多字不识,念不上句,所以开始时,师父就先从教学经典识字起步。观里有一本《康熙字典》,不会的字就让徒弟查。学的第一本经典是《太上说常感应篇》,就是现在的《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对周的人生观和影响最大,至今仍然能够背下来。所念的经是早、晚功课经合在一起的。其中《早功课经》的经文是大道洞玄虚,有念无不欺;炼质入仙真,随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无苦解;习归太上经,净念稽首礼。《晚功课经》是:重重无名是苦根,苦根除尽善根存。但凭慧剑威神力,跳出轮回无苦门。道以无心独有情,一切方便是修真。若归圣智源通理,便是升天得道人。
师父给徒弟讲解了经文的含义以后,就不在炕上学了,一定要到大殿老君像前敲着木鱼吟诵。师父恪守古制,每天在晚功课中唱诵这些经文。唱诵时师父左手敲木鱼,右手击鼓,按照固定的节奏和曲调进行,整个过程节奏舒缓、曲调和雅。周以后在学习其它的经典时,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下来。
周出家半年以后,师父开始系统地教授他学习道家经典,所用的课本就是神清观里的《道大藏经》。这时的教学地点也在大殿里。历代祖师们精心保护这套经书,使用的时候怕用手翻污损书籍,都是用竹签页一页翻的。《道大藏经》虽然经历了几百年,仍然没有大的损坏。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容易,既要经常使用,还要精心保护。
关于静坐的要领,师父是这样讲的:“仰面起邪火,低头阴水生,腰弓不通气,闭目阳不升。”即静坐时两眼不可闭紧,因为两眼闭紧了,容易发生很多弊病,出现很多阴境,所以二目要呈垂帘状。这些东西现在都公开了,很多书上讲的也很详细,但很多人做的并不对,主要原因是没有老师现场指导。
有人问周还有没有深入往上的功法,周老实地告诉大家,没有。当年师父教的就是这些。周一生就是靠着这点看着不起眼的东西,几次跳过鬼门关,活到今天。周认为现在的人好高骛远,不肯在最简单的地方下功夫,其实最初的就是最后的。周不否认可能有更深一层的功法,但没有清净戒律作基础只能学出一身毛病,起码不会长寿。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在圆寂时,弟子问他走后世人如何修行,他回答“以戒为师”。真正的佛教、道教的修行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当初师父到处找有心出家的小道士,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找一个做饭的伺候自己。师父直到临终的前一天还能够行动自如,能够自己照看自己。他找徒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昆嵛山道医的这门手艺传下去。因此师父在教周学习时督促甚严,他担心有生之年不能把龙门派医术传下去,对不起历代祖师。
也许师父已经预感到未来时局的艰难,有一次闲聊肘,他看似无意地对徒弟说:“将来的时局要有大的变化,观里恐怕呆不长久了,我教你学道医吧,一来你自己以后可以有个吃饭的本事,另外这也是咱神清观龙门派一脉独传的道门医术。”听说师父要教医术,周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师父很郑重地告诉周说,昆嵛山龙门派道医传到他这里是第四代,希望徒弟好好认真学习,不要怕吃苦,将来机缘合适时,要发扬光大这一道门医术,为民造福,一定不要让它失传。
周培明的道医技艺是宫师父手把手,一对一教出来的,是师父的亲传。
周培明出家的第一年,白天主要以学习做饭、打扫清洁、晚上学识字为主。当有了识字的基础后,第二年就开始在师父的指导下,学习道医的第一部经典《伤寒论》,第三年开始学习《金匮要略》,第四年学习《温病条辨》,第五年学习《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一书是穿插在中间,结合着上山采药学的。
周培明就是在学完了《温病条辨》以后开始独立行医的。在这之前几年,他一直都是跟随师父,边干边学。开始只是帮助抄写药方、配制草药等。抄写药方是中医师父带徒弟的主要方法,是师父言传身教的主要手段。由于平日经常有人慕名到观里请老道长看病,所以周很快地就学会把脉、舌诊、配方剂等技术。到后来,有了病号,师父就常常先让徒弟看,看完了他再给审查一遍,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他就纠正过来,待病人走后,重新给徒弟仔细分析、讲解错在何处,应如何正确诊治,并及时传授道医诊疗的相关要领、诀法等窍门。周的医术进步很快,也慢慢得到师父的认可。
师父还传给他一本老的《汤头歌诀》书,那书看样子能有一百多年,书里的纸张都已经发黄了,里面收录340多个药方。后来周又往里添加100多个,共计有400多个方子。2000年前后,有个烟台人向他借阅。后来她说不小心给弄丢了,还了周一个复印本。其实方子是死的,怎么辩证活用才是精髓。
神清观道医传下来很多的方剂剂型,到周来神清观时,很多的剂型已经无力制作了,只能尽能力制做一些相对简单的。但那些方子的配伍周都记了下来。
道医治病的一个特点是需要病人对生活有正确的态度,但很少有人把生活态度当成一个治病的方法。一个人没有了烦恼,心平气和了,身体的能量才会积聚、运行起来,去修复体内受损的部分。还有一点很重要,道教中人对疾病讲究的是预防,并不是治疗,强调“治未病”。因为预防是一种积极而主动的行为,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而治疗则显得被动,况且有些病也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道家养生讲究“治未病”,也就是防忠于未然。一个修道的人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你入门修炼的就是对自身及外界的这份敏感,道教的根本理论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法则,这个法则用于人身就是养生和预防疾病。丘祖的《摄生消息论》就是专门讲这方面内容的,其中按四季对应脏腑的不同分为春夏秋冬摄生消息,内容具体而丰富。
学道医难啊!道医与普通中医在医理上、治疗的方子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在修持上,道医学最核心的东西叫内证学,有守一、守窍、守呼吸等许多方法。在这一点上周认为自己只是有一点小体会,所证有限。
到山里采药,是周和师父每年必干的一件事。采药首先要认药,要知道每一种药材长的什么模样,在哪里有分布,认识它的生长环境。不同的药,喜性不同,有喜干燥的,有喜潮湿的,有生长在前阳的,有生活在背阴的,有喜湿气接近水的等等,都要清楚。
中药材有几千种,昆嵛山道门常用药材也就两三百种。药材的合理采集不仅可以保证药材的质量、药效,而且对保护、扩大药源也很重要。周认识中草药都是师父亲临现场言传身教,所以周对各种药材的分布地点、寻找方法以及药性的特点、采集的时间、炮制的方法等等都了然于心,特别是对一些珍稀药材的寻找,尤为熟知。如今在昆嵛山里还坚持采药的几位老人,当初都跟周学过。
按昆嵛山龙门派道医历代传下来的规矩,师徒所采的草药从来不外卖,全部用来给病人治病,从不收钱。就是到外面去买来的药,用于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也是一分钱不收。
师父是1943年6月间去世的。在去世前的十多天自身就有了感觉,不能再上山了,周也感觉到他的体力明显下降。一天早晨,师父把周叫过来,作最后的叮嘱,然后自己到房间里休息了,到中午时就去世了。当时他的身体呈吉祥卧姿态,安详地躺在那里。在整理好师父的遗容后,周就下山找来几个熟人帮忙,把师父放进棺木里,抬到山下神清观历代道士的公墓,按照辈分次序,把师父安葬了。
师父羽化后两个月,周便按照师父的嘱托,找到当时牟平城里“天春堂”(西门里)药铺的老板,去学习认识昆嵛山以外的中草药。师父在去世前曾对周说过,光靠昆嵛山的中草药治病是不够的,还要认识其它的中草药才行。“天春堂”的老板和师父是老关系,有时他也跟师父请教一些治病的方法。周在“天春堂”一共呆了大约七个月,期间也偶尔回到观上住,还发生了被三次动员还俗的事情。
到1944年秋天,周最后一次返回神清观,带上观里剩下的一些中草药和八宝坤顺丹、益母膏等成药,来到玉林店镇的大屯圈村,开始自己开药铺谋生。此后,神清观就荒废了。这期间,经人介绍,他和徐士文结为夫妻。她小周六岁,是给她父亲治病时认识的。结婚后,在老家椁椤村的西庵上安家,育有四女二男。一直到1994年才从庵上搬进村来。老伴于2006年冬去世,时年86岁。
1947年,周被动员参加支前的民工队伍,负责救治伤员。当年11月复员继续开药铺,后到昆阳区药社(就是后来的莒格庄医院),以后又参加合作医疗。1958年县卫生局调周到省中医学院进修一年。1959年学习回来后,被分配到威海温泉疗养院(山东省总工会所属)任保健医生。1965年开始,县卫生局调周参加乡村五期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周尽力把学的东西传给他们。1976年,周又被返聘到水道医院,帮助教学一年,后来又到莒格庄医院坐堂四年。辞了在医院的工作,在家里给老百姓免费看病、开处方,让病人自己拿着周的方子到药铺抓药,给患者节省了大笔治疗费用。
周现在91周岁了,还在不停地学习,看病、开方子。每当想起这一辈子能有机会帮助这么多人,和这么多人结缘,心里总是乐滋滋的。(选自刘学雷著《昆嵛道医——神清观末代道士访问记》)
相关地名
周法静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