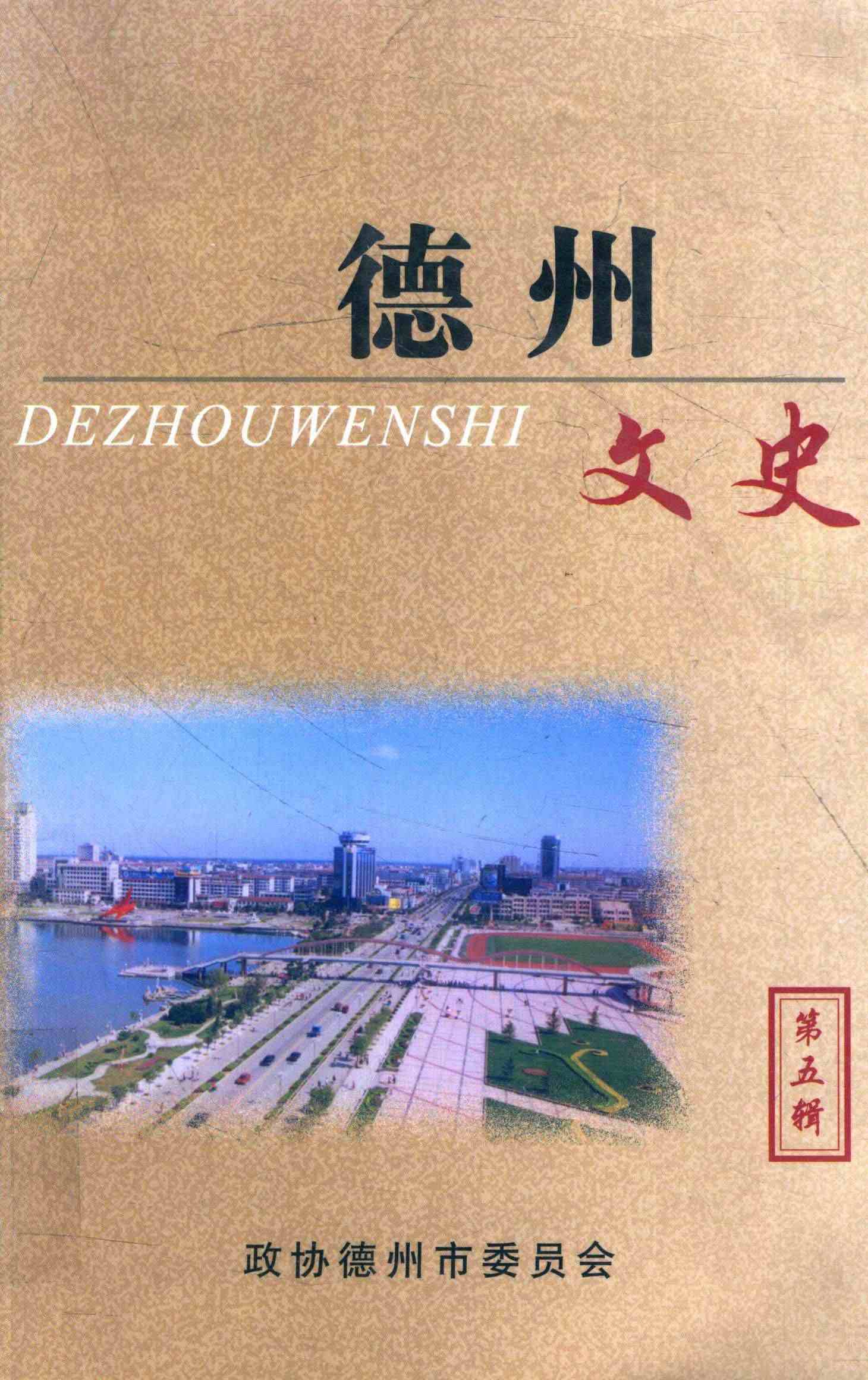话说德州老行当
| 内容出处: | 《德州文史》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7981 |
| 颗粒名称: | 话说德州老行当 |
| 分类号: | K250.652 |
| 页数: | 18 |
| 页码: | 315-332 |
| 摘要: | 无论今天是有是无,这些老行当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德州的历史文化和群众的生活状况,对我们开发人文资源和扩展就业门路,无疑是有益的。老年间,许多生活用品都是铁制的,如刀、剪、锅、鏊、锄、镰、锨、镢、犁耙、烙铁等等,因此铁匠这个行业很流行,也很吃香,生计当然也很辛苦。铁匠的作坊,简单的用独轮车推着,每到一村,找块树阴或空地,架起洪炉,支起铁砧,就可开张营业。不过,有些铁器制品还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扒钉、铁铲、耙齿、铁筷等等。独轮车又称羊角车、小红车。 |
| 关键词: | 德州市 老行当 |
内容
行当即行业。这里介绍的老行当,有些是德州特有的,有些是广泛存在的;有些已经成为历史,不复存在,有些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今天是有是无,这些老行当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德州的历史文化和群众的生活状况,对我们开发人文资源和扩展就业门路,无疑是有益的。
铁匠
老年间,许多生活用品都是铁制的,如刀、剪、锅、鏊、锄、镰、锨、镢、犁耙、烙铁等等,因此铁匠这个行业很流行,也很吃香,生计当然也很辛苦。
铁匠的作坊,简单的用独轮车推着,每到一村,找块树阴或空地,架起洪炉,支起铁砧,就可开张营业。大一点的作坊,被称为打铁铺或铁匠炉,在城镇或集市上有固定店铺,铺面都不大,一座铁叶棚子或两间破土房,中间盘个洪炉,架只大风箱,炉前就是铁砧。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锻打的铁件烧红之后,师傅一手钳住放到铁砧上,一手握小锤轻轻一点,指示着锤打的方位,徒弟则抡起大锤,当的重重地一击,火星四溅。师傅根据锻打的情况,不断翻动着钳着的铁器,叮当叮当之声便很有节奏地响着。在师徒二人的锤下,坚硬的铁块变得面团儿似的,要方即方,要圆即圆,要长即长,要扁即扁,或刀或叉,或锥或斧,定型之后,抛到旁边的水槽里,哧的一声烟雾蒸腾,淬过火一件产品就完成了。过去,小小的铁匠铺也打出过知名品牌,如北京的王麻子刀剪,上海的张小泉剪刀,名贯中华,多年产销两旺。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许多先进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代替了粗糙笨重的铁器制品,像王麻子刀剪这样知名的品牌,由于工艺落后和管理不善,企业也走向亏损和倒闭之路。
不过,有些铁器制品还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扒钉、铁铲、耙齿、铁筷等等。时下饭庄酒楼满街都是,而找个铁匠铺却是极难。正因为少者为贵,铁匠如今也成了香饽饽,是一门发家致富的好技术。我有一位亲戚,至今以祖传铁匠手艺支撑门面,生意兴隆发达,在镇上一口气盖起两座二层小楼,一个儿子一座,也都打铁,又添置了鼓风机、电锤等机械设备,生意更加红火,是当地富户之一。
吹糖人
吹糖人虽然是小本生意,却是一门技艺高超的行当,或祖传,或学徒,没有无师自通的。
吹糖人的多是一担挑。挑子前面是一个圆笼,笼内放一小煤炉,炉上蹲一只加盖的小铁锅,锅内有熬好的麦芽糖,炉火微微,甜气飘飘,金黄的糖稀只有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吹得成糖人。圆笼上钉一H形木架,既可挂扁担,又可把吹好的糖人插在上面,向众人展示。挑子后面是分层的木箱,放着煤球、竹签、勾铲、破蒲扇之类的杂物,摆摊时移过来当凳子坐。一担挑的家当必须少而精,一物多用,否则一路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力气干活儿。
吹糖人首先要熬好糖稀,熬欠了没劲儿,吹不成,熬过了不鲜亮,发脆,也吹不成。糖稀里掺什么、怎么熬,没有师傅指点是摸不着门的。吹糖人的时候,揪一块糖稀在手里,反复团揉,抻拉,待到糖稀作弄熟了,牵出一根细细的糖线儿,一边轻轻吹,一边在鼓起来的糖团上用手捏着各种形状,于是便有小猫、小狗、葫芦什么的呈现在眼前,还可以吹出孙悟空大闹天宫、胖娃娃骑金鲤和小老鼠偷油吃的故事来。如果要颜色,就把糖稀调和成红、绿、粉、蓝……吹出来的糖人或瓜果梨桃更是鲜艳无比,栩栩如生。这手上的活儿,看着容易做着难,绝非一日之功。
吹糖人的不用吆喝,手敲小铜锣,当当当一响,许多孩子便围拢过来。这种景象,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常见,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大约在五六年前,街头突然来了一个吹糖人的,围上来的不仅有孩子们,还有大人们,拥拥挤挤地占了半个街口。吹糖人的是一位老者,一身土气,满脸沧桑,两只粗糙的大手竟然摆弄出那么多生动的形象,大人孩子们稀罕得不得了,纷纷争购,老人简直吹不上卖,一锅糖稀不多时告罄。老人点着花花绿绿的票子,喜上眉梢。吹糖人是一项优秀的民间艺术,也是一个本小利大的经营项目,如今眼看着要失传了,实在可惜。
独轮车夫
千百年来,独轮车一直是大众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独轮车又称羊角车、小红车。车身为“凸”字形木架结构,中间装有一个木轮子,卡在两个木耳子之间。以前乡间道路狭窄,凹凸不平,泥泞难行,有的甚至是沟上崖下,弯弯曲曲,如羊肠小道,双轮大车根本无法通行,惟有独轮车才可穿行,这大概是独轮车兴起的原因吧。
独轮车必须保持两边平衡,才好驾驭。坐人要一边一个,载货需两边均等,如果只坐一人,另一边就要放上行李包裹或土坯石块什么的,偏沉了推起车来吃力还不稳。推车人两手握把,肩搭襻带,走起来肩、腰、臀、腿要灵活协调地扭动,才能在吱呀吱呀的欢叫声中平稳前进。那扭动的身躯是力与美的结合,被民间舞蹈吸取进秧歌中的老汉推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独轮车具有光荣的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的人民推着独轮车支前,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当年,德州人民用独轮车装着小米和弹药,推过淮海,推过长江,一直推倒蒋家王朝,推出一个新中国。
解放后,在生产建设中,独轮车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防旱抗涝,开河挖渠,千千万万民工推着独轮车上阵,上上下下,穿梭来往,为大兴水利立下汗马功劳。在车站、码头,搬运工人运煤送货,也是推着独轮车,汗流浃背,一字儿排开蔚蔚壮观的长龙阵。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独轮车的木轮换成了钢圈胶轮,安上轴承,推起来没了叫声,十分轻快,人们就管这种独轮车叫“推不够”,那种摆脱劳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推不够”也不多见了。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在平坦笔直的柏油路上,奔驰着拖拉机、农用汽车和机动三轮车,而私人大货和小轿车也日渐多了起来。要想见独轮车,只有去博物馆了。
布贩子德州盛产棉花,棉花多,纺纱织布的就多,织的布自己穿不了,需要赶集上店去卖,布贩子便应运而生了。
过去布贩子也叫卖大布的,盛行于现代纺织工业未发达之前。那时的布都是手工织的,叫土布。后来机织的布叫洋布。布贩子走村串户,收购土布,集中起来,运往城里,转手卖给染坊或布店。也有沿街叫卖的,虽然吃苦受累一些,可是能多赚到几个钱,这对于那些小布贩子来说也是值得的。
卖大布的主要指的是那些长途贩运的布贩子。他们车拉船载,把大量的布匹运往江南,或批发或留给自己的经销人。南方虽然盛产丝绸,可是价格昂贵,普通劳动人民穿戴不起,他们还是喜欢经济实惠的土布。更有胆大的经营者,竟把土布贩到南洋去卖。我读过一本有关缅泰的历史书,记得上面有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几个卖大布的富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夏津人,他是雇用马帮,翻山越岭把布匹驮到那里去的,如果途中不遇打家劫舍的强盗,不发生意外,一次就能赚回几年也享用不尽的金银财宝。
自从19世纪末纺织工业进入中国之后,土布渐渐被洋布所代替,不仅城市里布店多起来,乡村集市上也有了小布摊,布贩子的生意就日渐萧条了,可是总没有绝迹,在偏远的山区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直到新中国诞生,供销社遍地兴起,布贩子才在生活中消逝了。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天灾人祸又把我们逼到困难时期,粮布紧缺,实行计划供应。此时,布贩子又死灰复燃,不过,他们贩运的不再是布匹,而是布票。后来,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又丰富起来,不用你去管,市场自然就把他们淘汰了。
货郎
老年间,乡村没有商店,到有集市的地方去,也要十里八里,人们购物极不方便。特别是缠足的妇女,走不得远路,而生活中又离不开那些针头线脑之类的物品,因此,走村串巷的货郎便受到人们——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只要听到货郎鼓一响,她们就纷纷走出家门,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
货郎有挑担的、手提的、肩背的、推车的,不论用什么工具送货下乡,他们手中都摇着一只货郎鼓。那货郎鼓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至今还是孩子们的玩具或收藏家的珍品。鼓与鼓也不同,有单鼓的,有一鼓一锣的。鼓和锣都不比一只烧饼大,上面系一条皮绳锤子,推动起来,锣鼓齐鸣,双音清脆,煞是悦耳动听。
货郎一般不卖大件商品,多半是妇女喜欢的针头线脑、毛巾袜子、鞋面布料、木梳镜子、提鞋巴子等等。然而,就是这样的小东西,穷乡僻壤的百姓买起来也是惦量了又掂量,挑拣得格外细心。有的拿不出现钱,就用鸡蛋,粮食换,好心的货郎往往能将就也就将就了。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不知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得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乡镇有了供销社,村里有了代销点,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老全姓购物十分方便了,货郎也就自生自灭,不过,货郎送货下乡,那种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精神,却不能丢失,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成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三下乡活动的强大动力。
磨刀匠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有个磨刀人的角色,他那句似喊似唱的“磨剪子来——戗菜刀”,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过去,磨刀匠都是这样沿街吆喝,现在却轻易听不到这声音悠扬、节奏响亮的吆喝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破军号吹出来的刺耳的响声。
剪子、菜刀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也离不开的用具。因为经常使用,便容易刃卷锋钝,需要磨一磨,戗一戗,而自己缺这少那,往往费了力气还磨不锋利,就不如花几个小钱请磨刀师傅了。看来,磨刀匠这一行还是很需要的。
磨刀匠扛一条板凳,背一只褡子,板凳上固有粗细两块磨刀石,褡子里装着戗子、小锤子、钳子等几样工具。来了生意,放下板凳,坐下就干活,简单方便,不用找什么场地,也不用花本钱、学技术,只要吃得了奔波之苦,谁都可以干,而且不须营业执照,不纳税,收入虽然不多,平时混饱肚子不成问题,赶上年节,还能发点小财。农闲期间,出来转悠一阵子,既能贴补家庭,又权当徒步旅游,何必闲在家里打牌搓麻学不正经。
磨剪子戗菜刀技术故然简单,但做起来也需用心尽意。一般的刀剪先在粗石上磨,后在细石上磨,才能磨得又亮又锋利,人们常以吹毛即断来形容。刀与剪的种类很多,如菜刀、砍刀、剁刀、水果刀、牛耳刀、剃头刀……绣花剪、裁衣剪、羊毛剪、理发剪、空口剪……最大的料剪几斤重,最小的花色剪一寸长。磨刀匠要了解各种刀剪的性能,有的戗一戗就行,有的要在粗石上狠狠地磨,有的只能在细石上轻轻地磨,该重的不重,该轻的不轻,不仅磨不好活儿,还容易葬弄家什,臭了自己的名声,生意就不好混了。
锢漏匠
锢漏匠,是锔盆子锔碗锔大缸的工匠。过去,无论在乡村或城市,大多数劳苦群众都很贫穷,使唤的盆子、碗破了,舍不得扔掉,等锢漏匠来了锔上再用。
锢漏匠挑着担子,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走许多路,扁担必须轻巧、灵便,一步一颤,不死沉死沉地压在肩上。挑子的前后,各吊着一面巴掌大的小铜锣,随着扁担的颤动,不停地摇摆着,一路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告诉人们锢漏匠来了。
锔盆子锔碗没有固定的价格,要根据瓷器的粗细好坏,用锔子的大小多少和破裂的情况而定。讲好价钱才能做活。锔碗一般都用金刚钻。先取出一条细长的绳子,把绳头的钩子钩住碗边,再将破碗拼接好,用绳子紧紧地反复捆扎起来,然后夹在双膝之间,开始用钻打孔。钻弓的弦是一条细皮条,绕着一个下端镶有金刚钻的钻头,匠人来回拉动弓弦,钻头随之不停地转动,就在碗的破缝两边均匀地打出两排小孔。这时,再从担子的小抽屉里取出铜制的小扒锔儿,手操钉锤,轻轻地打入孔中,一个个都钉瓷实了,在裂缝处抹上白瓷膏,大拇指一察,这碗就算锔好了。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你这瓷器活。”讲的就是只有米粒般小的金刚钻,却是锢漏匠最贵重的家什,用起来格外当心。锔盆子锔大缸,粗瓷或瓦的就要把金刚钻换下来,用三棱针一样的钻头,打出的孔又深又大,才能把水缸或面盆锔牢。不管是金刚钻还是针头钻,转动起来钻孔时都会磨擦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所以有人说锢漏匠是因为这声音而得名。
小时候看过锔大缸的戏和舞蹈,至今还有深刻印象。舞蹈是通过小锢漏匠的热情服务而赢得村姑的一片芳心,表现出劳动人民纯朴美好的爱情。戏剧则以小丑演锢漏匠,男旦反串老大娘,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但相互调情逗乐,却也幽默风趣,令人捧腹。现在,这种节目还在演出,而锢漏匠却不见了。如今别说碗打破了,就是有个豁口裂道璺,人们也毫不怜惜地会把它扔掉。即使有保存价值的古瓷器,坏了也不用锢漏匠来锔,随处可以买到化学粘合剂,粘起来丝毫看不出破绽,如同原物一样。我想,锢漏匠的技术无论多么精,也会自愧弗如,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弹棉花
弹棉花这一行,虽然很土很古老,可是至今昌盛不衰。你走在彩灯闪烁,繁忙喧嚣的街市中,时而会听到嗡嗡的响声,循声而去,一座简陋的弹棉花作坊就会出现在面前。
弹棉花用的主要工具是一张弹性极强的大木弓,约五六尺长。木弓下端绑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插在腰背后的皮带中,另一头通过头顶,吊在竹筷般粗的大木弓的牛筋长弦上。弹棉花时,右手拿木棰敲击牛筋长弦,发出嗡嗡的响声,长弦不断震动,就把原来压得板结的棉套弹得篷松暄腾了。
棉衣、棉被用过多年,里面絮的棉花藏污纳垢,死死板板,弹起来尘埃弥漫,游丝飞舞,是个很脏很累的活儿。即使戴上口罩,系紧领口袖口,眉毛胡子上还是沾满飞絮,乍一看就像老寿星似的。过去,干这种活儿的,多数是忙完秋赶到城里来的乡下人,趁着换季的时候,忙上一个多月,挣几个钱回去准备过年。现在弹棉花转向职业化,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累月有忙不完的活儿。人们富裕了,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为了睡得舒服一点,穿得暖和一些,不惜弹棉花花那几个钱。
按说,北方寒冷,棉衣棉被用得多,从事弹棉花这一行的人也该多,可是,近年来出现在德州街头的弹棉花的,十之八九却来自南方,有的甚至来自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他们不恋故土,远走他乡,能吃苦,善经营,而且知道自己的长短,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大钱能赚,小钱也不放过,勤劳致富,积少成多,而且没有什么风险。这种精明而又灵活的经商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纺棉花
一盏油灯,一架纺车,寒冬深夜,嗡嗡的纺车声送我入梦。妈妈纺棉花的影子,至今常常在我记忆的荧屏上闪现。
纺棉花也叫纺线。木制的纺车,由一只大纺轮带动一支小锭杆儿。纺线时先要把棉花搓成油条似的布剂,捏在左手里,然后右手摇转纺车,把布剂从飞转的锭杆上引出线来,大约纺出多半尺长,绕在锭杆上,再纺。如此反复,锭杆上就绕出一个鸭蛋似的线棰儿,卸下来,放在瓦罐儿里。瓦罐儿里一般还放着鸡蛋,要轻拿轻放,不仅线棰儿抖搂不了,还能保护鸡蛋不被磕破,真是一举两得。纺线多是为了织布,但一般人家没有织布机,等线棰儿攒够一定数量,就和鸡蛋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儿零钱,打个油盐酱醋什么的也不作难了。过去,这是农村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
千百年来,我国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纺线织布也就成了农村妇女的主要劳动项目。正像古装黄梅戏里七仙女与董永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和现代评剧《刘巧儿》中唱的“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那样,男女分工合作,夫妻恩恩爱爱,生活虽苦心里也觉得甜。在德州地方戏中,乐陵哈哈腔有一出《摔纺车》的传统剧目,讲的是不务正业的刘二嘎,在外赌输了钱回家拿老婆出气,挨打挨骂老婆都忍了,可是摔坏了纺车,等同断绝了一家人的生路,老婆便忍无可忍地与刘二嘎大吵大闹起来。她发自肺腑的哭诉,终于使刘二嘎回心转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出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纺棉花在小农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难怪那时会有“家家纺车转,户户纺车声”了。
纺棉花不仅在小农经济中举足轻重,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几百架纺车在窑洞前一字儿摆开,男女八路军战士一齐动手,自己纺纱织布做军衣,挫败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当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坐在纺车前纺过棉花。如今,这一架架简单的土纺车,成了革命文物,放在博物馆里,吸引着无数后人景仰的目光。
旋锭杆
纺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就是锭杆,这部件又很爱坏,一架纺车往往要备用两三支,所以锭杆的需求量非常大,旋锭杆也就成了一个热门行业。
旋锭杆也叫铣锭杆。铣,这个现代工业的技术用语,大概就是从落后的手工业中学来的吧。锭杆是一尺来长,两头尖细,中间略粗并旋有凹槽儿的一个木轴儿,纺轮带动它转起来,才能纺出纱线。由于长期不断地旋转,尖细的两端很容易磨损,失去光滑而跳动不稳,必须换支新的。
旋锭杆的木料很讲究,质地松软的杨、柳、杉等不能用,最好是檀木、枣木、梨木也行,顶不济也得是槐木、榆木,只有木质坚实细腻,旋出的锭杆才光滑好使,经磨耐用。一支锭杆的价码,完全根据木料的好坏而定。如果谁家有一支檀木锭杆,简直成了宝贝,不用时摘下来包在棉花里,生怕碰坏了。有人来借纺车,这支锭杆一般是不会外借的。
旋锭杆的并非只旋锭杆,也旋擀面杖或捣蒜棰子,反正用一套工具,旋的都是木制品,技术操作也差不多,为了养家糊口,为什么能挣的钱不挣呢?
每到年节,他们还旋一些陀螺或冰尜,拿到集市上去卖。冰尜大的如蔓菁,小的如鸡蛋,有一头尖的,也有两头尖反倒都能转的,上面刻着图案或涂着颜色,在洁白的冰雪上旋转起来,美似一团绽放的花朵,很受孩子们的喜爱。抽冰尜要不断扬起手臂,跟着飞转的冰尜跑来跑去,是冬季进行户外活动,加强体育锻炼的好方法。如今旋锭杆当然没了市场,可是旋冰尜作为少年或老年人的健身器材,还是可以开发利用的。
吹鼓手
吹鼓手,现在也称吹奏班子或音乐队,受雇于红白喜事,在我区各县市普遍流行。一个班底有四至八人,主要乐器是唢呐,配以笙、笛、二胡、小锣小鼓等。一个好班子,不仅会演奏各种曲牌,还会唢呐卡戏或演唱。大户人家为了摆阔寻热闹,有时雇来两三套班子,相互竞技赛艺,引得围观者喝彩声不绝,煞是喜庆火爆。
按行规,吹鼓手和唱戏的是一家人,不论相识或不相识的,见面即称兄弟。剧团演职员在行军赶路时,如果听到村里有鼓乐声,赶了过去就被让到上座,会吹的吹,会唱的唱,即使是管服装道具的,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照样吃吃喝喝、混个酒足饭饱。
“文革”期间破四旧,吹鼓手被视为封建文化而遭禁,老百姓办红白喜事不能没动静,就支起大喇叭放录音。然而,吹鼓手的作用有些是大喇叭很难代替的。那时乡村用电尚不普及,没有电大喇叭不响,死气沉沉,喜事办得不喜庆。而办丧事,陪棂的人不能老跪在那里哭,吊唁的人来了要及时通知陪棂的人,吹鼓手在门外一吹号就行了,没有吹鼓手得安排专人通风报信,那人一不留神误了通报,没有人陪棂你说尴尬不尴
尬!
过去吹鼓手被视为下九流,新社会被称为民间艺人,社会地位提高了。乐陵市刘凤祥,从小随父当吹鼓手,练就一身本领,30岁应聘为沈阳音乐学院教师,“文革”中被赶回家,仍在民间从事演奏活动。他吹的唢呐优美动听,技艺超群,被群众誉为“吹破天”,成为县政协委员。他曾多次参加省市文艺会演,1980年代表德州晋京出席农民文艺会演,他的唢呐独奏《百凤朝阳》和卡戏河北梆子选段,获优秀节目奖,被拍摄成艺术片,他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刘凤祥从此名声大振,周围县市许多人都慕名前来邀请,出价比一般吹鼓手要高几倍。
我市过去有一位县文化局长,曾当过剧团团长,能唱几口河北梆子。县剧团解散后,几个艺人组成演奏队,邀请退休的老局长参加,老局长耐不得寂寞,应邀当了吹鼓手。许多老百姓认识他,见老局长来了,觉得很长脸,格外光彩,不仅开价特别高,而且老局长唱上两段之后,就赶紧把他请到上席,待为贵宾。你看,名人效应就是非同一般,不服不行。
杂耍
德州是杂技之乡。据宁津县有关史料记载,黄家镇杂技古会,每年八月十五至九月十五举行,省内外许多杂技班都来这里汇集,各种杂技道具也在这里出售,还可拜师学艺,选人组班,散会后各奔东西,走江湖,卖艺为生。仅这个县张鳌乡野竹李一村,就有近百个大小杂技班子,400多名杂耍艺人,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拿起家伙来,人人有一手。”
杂耍是杂技艺术中的基础项目,主要是手技、蹬技、顶技、口技、车技、踩技等,一个人即可撂地,几个人也能摆场,大小随意,行动便捷,演出机动灵活,这是德州最具传统特色的老行当。
杂耍艺人以一家一户为主,杂有亲朋或学徒。每到一地演出,条件好的围一圈布账,卖票,条件差的就地打个场子,演俩节目敛几个小钱。杂耍艺人一般都是多面手,能文能武,浑身功夫,几个人轮番上阵,大半天演出不会重样儿。当然,为了等待观众,拖延时间,演出前每每要说一阵闲话,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玩艺儿是假的,功夫儿是真的”等等,嚼来嚼去,磨得人耳朵眼里生茧子。为了迎合观众的好奇心和换得人们的同情,多赚几个钱,有些艺人不惜铤而走险,演出吞剑、大卸八块等残酷恐怖节目,有人不慎丧了性命。人们都说演出这种节目的孩子,不是父母亲生的,是偷来或拐骗来的,否则,哪有这样狠心的父母?其实,人们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旧社会杂耍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欺压凌辱,为了生计不得不赌上身家性命。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禁演了一批惑淫惑盗和血腥恐怖的节目,危害杂耍艺人身心健康的吞剑,大卸八块等也很快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创意新颖的优秀节目,如《快乐的炊事员》、《抢椅子》、《机器人》等等,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耍猴
在宁津县黄家镇杂技古会上,有许多买卖驯养小动物的,如猴子、狗熊、山羊、小狗……特别是有灵性的猴子,买上一只牵了去,走江湖,耍把戏,天南海北,漂洋过海,度过风雨人生。
耍猴的多为单身,也有带着老婆孩子的,在乡村集市或城镇广场打个园场,敲一阵锣,冲着围拢来的人作一圈箩圈揖,说一段“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之类的开场白,便开始耍猴了。有的猴子光身儿,有的猴子穿衣戴帽儿,一副人模狗样的,先给大家敬一圈儿礼,活蹦乱跳的,很是乖巧可爱。猴子表演的节目好坏与多少,全看主人驯化的功夫。有的猴子会钻火圈、骑羊、耍刀舞棍,还有的会扮作孙悟空或醉汉,时而憨态可掬,时而活泼无比,令人欢喜,更令孩子们雀跃。可是,过去贫穷落后,围观的人不少,给钱的人不多,特别是孩子们兜里没有一分钱,只好把吃剩的地瓜、窝头或花生什么的扔过去,给捧着铜锣的主人或猴子。不管收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又饿又馋的猴子也不敢动,必须交给主人,等着赏赐,否则,主人手中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
耍猴游动性很大,哪里年成好能赚钱就往哪里去,城市乡村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如果你打听一下,十有八九是我们的老乡。在旱、涝、蝗灾连年不绝的旧中国,常常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鲁北人出去耍猴,却也闯出一条生路。如今,国泰民安,生活富裕,德州人民进入新世纪,正信心百倍地奔向小康之路,谁还为乞讨几个小钱去耍猴呢?
拉洋片
上个世纪之初,中国就有了电影,可是解放前,电影事业发展缓慢,只有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里才能看到,广大城镇和乡村的人只是听说过。那时,到处流行着拉洋片的,有人说这和看电影差不多,不少人便信以为真,拉洋片的生意就很快红火起来。
拉洋片需要一只大木箱,里面装上可以转动的画片,木箱前面开几个园园的小窗孔,通过凸透镜观看里面一幅幅不断变动的画片。拉洋片的人站在木箱的一侧,一手操纵画片的提线或转柄,一手拉动串连着的锣鼓,在叮咚作响的鼓乐声中,唱着画片的内容。唱腔多为当地民歌小调,唱词也通俗易懂,如“往里瞧来往里看,唐僧取经上西天,师徒来到盘丝洞,一个个美女赛天仙……”画片的故事一般都适合孩子们观看,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岳母刺字》等。但为了吸引成年人,也有《尼姑偷和尚》、《大姑娘洗澡》等低级下流的东西。不过,那样的画片只有简单的一两张,摊主也不唱内容,常常有托儿悄悄地看,偷偷地笑,让那些光棍汉子心猿意马,经不住诱惑,不得不把钱掏出来。因为价钱较高,这样的画片孩子们一般是看不起的。
拉洋片也叫西洋镜,这名称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其实不然。如果是从国外传入的,拉洋片的人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大城市里,而恰恰相反,他们多数是来自乡村。据一份文化资料记载,当时活跃在上海滩的拉洋片的人,以山东的农民居首。他们所以给这种把戏加上个“洋”字,无非是以洋代土,掩人耳目,多挣几个钱罢了。人们乍开始看西洋镜,还有点好奇,而一旦看过电影,便觉得大相径庭,受骗上当了,因此创造出“拆穿西洋镜”这个俗语,表示骗局或阴谋被揭露和识破的意思。解放后,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谁还去看那被拆穿的西洋镜呢!
说唱艺人
我国传统的说唱艺术,现在统称曲艺。表演者一人至三五人不等,有的只说不唱,如评书;有的只唱不说,如河南坠子;有的又说又唱,如大鼓;有的不说也不唱,只有表演,如双簧。形式多种多样,演出简单方便,只要求一桌或一椅,一鼓或一弦,一般不需特意化妆,更无需舞台布景,场边地头、室内露天演出均可,说唱通俗易懂,普及华夏大地,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说唱艺术在德州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城德州地处京津门户,运河要道,津浦石德铁路在这里交汇,是一个发达繁荣的水陆码头,也是各路艺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这里的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把各种演唱艺术融留下来。据不完全统计,在德州市上演过的曲种有: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木板大鼓、胶东大鼓、乐亭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天津快板、天津时调、快板书、渔鼓坠、数来宝、单弦、相声、评词、皮影、双簧等;而现代曲艺大师也有不少人来德州演出过,如骆玉笙、马三立、侯宝霆、侯宝林、郭启儒、马季、马增芬、马增慧、高思培、高元均、范振玉、孙金枝、刘兰芳、郭文秋、杨立德、孙少臣、孙振业等。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德州这块群众文化艺术的沃土上,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说唱艺人,武城著名琴师谢其荣,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曾为白妞、黑妞弹弦伴奏,看过《老残游记》的人都记得,白妞在济南明湖居演唱梨花大鼓的火爆动人场面。谢其荣熟谙白妞、黑妞清脆婉转、刚柔相济的演唱风格,严格教练女儿谢大玉,使其造诣颇深,成为继白妞、黑妞之后的梨花大鼓的优秀传人、名声远播京津沪宁及东北等地。乐陵鼓书艺人左玉玺,父子叔侄、胞兄胞弟,都演唱西河大鼓,且不断革新,自成一格,被称为鼓书世家。抗战期间,左玉玺因拒绝为汉奸演唱,惨遭毒打而亡。其侄左金魁继承叔父的人生品格和唱演技艺,为避顽匪威逼,潜回家乡,建国后参加省曲艺会演,荣获演唱一等奖,并当选省曲协副主席。此外还有禹城的曲艺作家张军及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夏津山东大鼓演员王长志等。
解放前,说唱艺人多数是散兵游勇,以演唱糊口谋生,被称为“要饭的买卖”。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说唱艺人组织起来,我区各县市普遍建立了曲艺队、曲艺厅,曲艺事业得到迅猛发展。上世纪50年代,德州市曲艺队有固定演出场所五处;夏津县曲艺队一度发展到100多人;1982年宁津县举办曲艺训练班,招考学员,应试者多达1500余人。广大的曲艺工作者,被称为文艺轻骑兵,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不仅说唱优秀的传统曲目,而且积极创作现代曲目,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一车高粱米》、《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设精神文明,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铁匠
老年间,许多生活用品都是铁制的,如刀、剪、锅、鏊、锄、镰、锨、镢、犁耙、烙铁等等,因此铁匠这个行业很流行,也很吃香,生计当然也很辛苦。
铁匠的作坊,简单的用独轮车推着,每到一村,找块树阴或空地,架起洪炉,支起铁砧,就可开张营业。大一点的作坊,被称为打铁铺或铁匠炉,在城镇或集市上有固定店铺,铺面都不大,一座铁叶棚子或两间破土房,中间盘个洪炉,架只大风箱,炉前就是铁砧。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锻打的铁件烧红之后,师傅一手钳住放到铁砧上,一手握小锤轻轻一点,指示着锤打的方位,徒弟则抡起大锤,当的重重地一击,火星四溅。师傅根据锻打的情况,不断翻动着钳着的铁器,叮当叮当之声便很有节奏地响着。在师徒二人的锤下,坚硬的铁块变得面团儿似的,要方即方,要圆即圆,要长即长,要扁即扁,或刀或叉,或锥或斧,定型之后,抛到旁边的水槽里,哧的一声烟雾蒸腾,淬过火一件产品就完成了。过去,小小的铁匠铺也打出过知名品牌,如北京的王麻子刀剪,上海的张小泉剪刀,名贯中华,多年产销两旺。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许多先进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代替了粗糙笨重的铁器制品,像王麻子刀剪这样知名的品牌,由于工艺落后和管理不善,企业也走向亏损和倒闭之路。
不过,有些铁器制品还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扒钉、铁铲、耙齿、铁筷等等。时下饭庄酒楼满街都是,而找个铁匠铺却是极难。正因为少者为贵,铁匠如今也成了香饽饽,是一门发家致富的好技术。我有一位亲戚,至今以祖传铁匠手艺支撑门面,生意兴隆发达,在镇上一口气盖起两座二层小楼,一个儿子一座,也都打铁,又添置了鼓风机、电锤等机械设备,生意更加红火,是当地富户之一。
吹糖人
吹糖人虽然是小本生意,却是一门技艺高超的行当,或祖传,或学徒,没有无师自通的。
吹糖人的多是一担挑。挑子前面是一个圆笼,笼内放一小煤炉,炉上蹲一只加盖的小铁锅,锅内有熬好的麦芽糖,炉火微微,甜气飘飘,金黄的糖稀只有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吹得成糖人。圆笼上钉一H形木架,既可挂扁担,又可把吹好的糖人插在上面,向众人展示。挑子后面是分层的木箱,放着煤球、竹签、勾铲、破蒲扇之类的杂物,摆摊时移过来当凳子坐。一担挑的家当必须少而精,一物多用,否则一路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力气干活儿。
吹糖人首先要熬好糖稀,熬欠了没劲儿,吹不成,熬过了不鲜亮,发脆,也吹不成。糖稀里掺什么、怎么熬,没有师傅指点是摸不着门的。吹糖人的时候,揪一块糖稀在手里,反复团揉,抻拉,待到糖稀作弄熟了,牵出一根细细的糖线儿,一边轻轻吹,一边在鼓起来的糖团上用手捏着各种形状,于是便有小猫、小狗、葫芦什么的呈现在眼前,还可以吹出孙悟空大闹天宫、胖娃娃骑金鲤和小老鼠偷油吃的故事来。如果要颜色,就把糖稀调和成红、绿、粉、蓝……吹出来的糖人或瓜果梨桃更是鲜艳无比,栩栩如生。这手上的活儿,看着容易做着难,绝非一日之功。
吹糖人的不用吆喝,手敲小铜锣,当当当一响,许多孩子便围拢过来。这种景象,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常见,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大约在五六年前,街头突然来了一个吹糖人的,围上来的不仅有孩子们,还有大人们,拥拥挤挤地占了半个街口。吹糖人的是一位老者,一身土气,满脸沧桑,两只粗糙的大手竟然摆弄出那么多生动的形象,大人孩子们稀罕得不得了,纷纷争购,老人简直吹不上卖,一锅糖稀不多时告罄。老人点着花花绿绿的票子,喜上眉梢。吹糖人是一项优秀的民间艺术,也是一个本小利大的经营项目,如今眼看着要失传了,实在可惜。
独轮车夫
千百年来,独轮车一直是大众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独轮车又称羊角车、小红车。车身为“凸”字形木架结构,中间装有一个木轮子,卡在两个木耳子之间。以前乡间道路狭窄,凹凸不平,泥泞难行,有的甚至是沟上崖下,弯弯曲曲,如羊肠小道,双轮大车根本无法通行,惟有独轮车才可穿行,这大概是独轮车兴起的原因吧。
独轮车必须保持两边平衡,才好驾驭。坐人要一边一个,载货需两边均等,如果只坐一人,另一边就要放上行李包裹或土坯石块什么的,偏沉了推起车来吃力还不稳。推车人两手握把,肩搭襻带,走起来肩、腰、臀、腿要灵活协调地扭动,才能在吱呀吱呀的欢叫声中平稳前进。那扭动的身躯是力与美的结合,被民间舞蹈吸取进秧歌中的老汉推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独轮车具有光荣的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的人民推着独轮车支前,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当年,德州人民用独轮车装着小米和弹药,推过淮海,推过长江,一直推倒蒋家王朝,推出一个新中国。
解放后,在生产建设中,独轮车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防旱抗涝,开河挖渠,千千万万民工推着独轮车上阵,上上下下,穿梭来往,为大兴水利立下汗马功劳。在车站、码头,搬运工人运煤送货,也是推着独轮车,汗流浃背,一字儿排开蔚蔚壮观的长龙阵。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独轮车的木轮换成了钢圈胶轮,安上轴承,推起来没了叫声,十分轻快,人们就管这种独轮车叫“推不够”,那种摆脱劳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推不够”也不多见了。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在平坦笔直的柏油路上,奔驰着拖拉机、农用汽车和机动三轮车,而私人大货和小轿车也日渐多了起来。要想见独轮车,只有去博物馆了。
布贩子德州盛产棉花,棉花多,纺纱织布的就多,织的布自己穿不了,需要赶集上店去卖,布贩子便应运而生了。
过去布贩子也叫卖大布的,盛行于现代纺织工业未发达之前。那时的布都是手工织的,叫土布。后来机织的布叫洋布。布贩子走村串户,收购土布,集中起来,运往城里,转手卖给染坊或布店。也有沿街叫卖的,虽然吃苦受累一些,可是能多赚到几个钱,这对于那些小布贩子来说也是值得的。
卖大布的主要指的是那些长途贩运的布贩子。他们车拉船载,把大量的布匹运往江南,或批发或留给自己的经销人。南方虽然盛产丝绸,可是价格昂贵,普通劳动人民穿戴不起,他们还是喜欢经济实惠的土布。更有胆大的经营者,竟把土布贩到南洋去卖。我读过一本有关缅泰的历史书,记得上面有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几个卖大布的富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夏津人,他是雇用马帮,翻山越岭把布匹驮到那里去的,如果途中不遇打家劫舍的强盗,不发生意外,一次就能赚回几年也享用不尽的金银财宝。
自从19世纪末纺织工业进入中国之后,土布渐渐被洋布所代替,不仅城市里布店多起来,乡村集市上也有了小布摊,布贩子的生意就日渐萧条了,可是总没有绝迹,在偏远的山区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直到新中国诞生,供销社遍地兴起,布贩子才在生活中消逝了。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天灾人祸又把我们逼到困难时期,粮布紧缺,实行计划供应。此时,布贩子又死灰复燃,不过,他们贩运的不再是布匹,而是布票。后来,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又丰富起来,不用你去管,市场自然就把他们淘汰了。
货郎
老年间,乡村没有商店,到有集市的地方去,也要十里八里,人们购物极不方便。特别是缠足的妇女,走不得远路,而生活中又离不开那些针头线脑之类的物品,因此,走村串巷的货郎便受到人们——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只要听到货郎鼓一响,她们就纷纷走出家门,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
货郎有挑担的、手提的、肩背的、推车的,不论用什么工具送货下乡,他们手中都摇着一只货郎鼓。那货郎鼓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至今还是孩子们的玩具或收藏家的珍品。鼓与鼓也不同,有单鼓的,有一鼓一锣的。鼓和锣都不比一只烧饼大,上面系一条皮绳锤子,推动起来,锣鼓齐鸣,双音清脆,煞是悦耳动听。
货郎一般不卖大件商品,多半是妇女喜欢的针头线脑、毛巾袜子、鞋面布料、木梳镜子、提鞋巴子等等。然而,就是这样的小东西,穷乡僻壤的百姓买起来也是惦量了又掂量,挑拣得格外细心。有的拿不出现钱,就用鸡蛋,粮食换,好心的货郎往往能将就也就将就了。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不知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得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乡镇有了供销社,村里有了代销点,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老全姓购物十分方便了,货郎也就自生自灭,不过,货郎送货下乡,那种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精神,却不能丢失,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成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三下乡活动的强大动力。
磨刀匠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有个磨刀人的角色,他那句似喊似唱的“磨剪子来——戗菜刀”,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过去,磨刀匠都是这样沿街吆喝,现在却轻易听不到这声音悠扬、节奏响亮的吆喝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破军号吹出来的刺耳的响声。
剪子、菜刀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也离不开的用具。因为经常使用,便容易刃卷锋钝,需要磨一磨,戗一戗,而自己缺这少那,往往费了力气还磨不锋利,就不如花几个小钱请磨刀师傅了。看来,磨刀匠这一行还是很需要的。
磨刀匠扛一条板凳,背一只褡子,板凳上固有粗细两块磨刀石,褡子里装着戗子、小锤子、钳子等几样工具。来了生意,放下板凳,坐下就干活,简单方便,不用找什么场地,也不用花本钱、学技术,只要吃得了奔波之苦,谁都可以干,而且不须营业执照,不纳税,收入虽然不多,平时混饱肚子不成问题,赶上年节,还能发点小财。农闲期间,出来转悠一阵子,既能贴补家庭,又权当徒步旅游,何必闲在家里打牌搓麻学不正经。
磨剪子戗菜刀技术故然简单,但做起来也需用心尽意。一般的刀剪先在粗石上磨,后在细石上磨,才能磨得又亮又锋利,人们常以吹毛即断来形容。刀与剪的种类很多,如菜刀、砍刀、剁刀、水果刀、牛耳刀、剃头刀……绣花剪、裁衣剪、羊毛剪、理发剪、空口剪……最大的料剪几斤重,最小的花色剪一寸长。磨刀匠要了解各种刀剪的性能,有的戗一戗就行,有的要在粗石上狠狠地磨,有的只能在细石上轻轻地磨,该重的不重,该轻的不轻,不仅磨不好活儿,还容易葬弄家什,臭了自己的名声,生意就不好混了。
锢漏匠
锢漏匠,是锔盆子锔碗锔大缸的工匠。过去,无论在乡村或城市,大多数劳苦群众都很贫穷,使唤的盆子、碗破了,舍不得扔掉,等锢漏匠来了锔上再用。
锢漏匠挑着担子,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走许多路,扁担必须轻巧、灵便,一步一颤,不死沉死沉地压在肩上。挑子的前后,各吊着一面巴掌大的小铜锣,随着扁担的颤动,不停地摇摆着,一路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告诉人们锢漏匠来了。
锔盆子锔碗没有固定的价格,要根据瓷器的粗细好坏,用锔子的大小多少和破裂的情况而定。讲好价钱才能做活。锔碗一般都用金刚钻。先取出一条细长的绳子,把绳头的钩子钩住碗边,再将破碗拼接好,用绳子紧紧地反复捆扎起来,然后夹在双膝之间,开始用钻打孔。钻弓的弦是一条细皮条,绕着一个下端镶有金刚钻的钻头,匠人来回拉动弓弦,钻头随之不停地转动,就在碗的破缝两边均匀地打出两排小孔。这时,再从担子的小抽屉里取出铜制的小扒锔儿,手操钉锤,轻轻地打入孔中,一个个都钉瓷实了,在裂缝处抹上白瓷膏,大拇指一察,这碗就算锔好了。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你这瓷器活。”讲的就是只有米粒般小的金刚钻,却是锢漏匠最贵重的家什,用起来格外当心。锔盆子锔大缸,粗瓷或瓦的就要把金刚钻换下来,用三棱针一样的钻头,打出的孔又深又大,才能把水缸或面盆锔牢。不管是金刚钻还是针头钻,转动起来钻孔时都会磨擦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所以有人说锢漏匠是因为这声音而得名。
小时候看过锔大缸的戏和舞蹈,至今还有深刻印象。舞蹈是通过小锢漏匠的热情服务而赢得村姑的一片芳心,表现出劳动人民纯朴美好的爱情。戏剧则以小丑演锢漏匠,男旦反串老大娘,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但相互调情逗乐,却也幽默风趣,令人捧腹。现在,这种节目还在演出,而锢漏匠却不见了。如今别说碗打破了,就是有个豁口裂道璺,人们也毫不怜惜地会把它扔掉。即使有保存价值的古瓷器,坏了也不用锢漏匠来锔,随处可以买到化学粘合剂,粘起来丝毫看不出破绽,如同原物一样。我想,锢漏匠的技术无论多么精,也会自愧弗如,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弹棉花
弹棉花这一行,虽然很土很古老,可是至今昌盛不衰。你走在彩灯闪烁,繁忙喧嚣的街市中,时而会听到嗡嗡的响声,循声而去,一座简陋的弹棉花作坊就会出现在面前。
弹棉花用的主要工具是一张弹性极强的大木弓,约五六尺长。木弓下端绑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插在腰背后的皮带中,另一头通过头顶,吊在竹筷般粗的大木弓的牛筋长弦上。弹棉花时,右手拿木棰敲击牛筋长弦,发出嗡嗡的响声,长弦不断震动,就把原来压得板结的棉套弹得篷松暄腾了。
棉衣、棉被用过多年,里面絮的棉花藏污纳垢,死死板板,弹起来尘埃弥漫,游丝飞舞,是个很脏很累的活儿。即使戴上口罩,系紧领口袖口,眉毛胡子上还是沾满飞絮,乍一看就像老寿星似的。过去,干这种活儿的,多数是忙完秋赶到城里来的乡下人,趁着换季的时候,忙上一个多月,挣几个钱回去准备过年。现在弹棉花转向职业化,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累月有忙不完的活儿。人们富裕了,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为了睡得舒服一点,穿得暖和一些,不惜弹棉花花那几个钱。
按说,北方寒冷,棉衣棉被用得多,从事弹棉花这一行的人也该多,可是,近年来出现在德州街头的弹棉花的,十之八九却来自南方,有的甚至来自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他们不恋故土,远走他乡,能吃苦,善经营,而且知道自己的长短,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大钱能赚,小钱也不放过,勤劳致富,积少成多,而且没有什么风险。这种精明而又灵活的经商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纺棉花
一盏油灯,一架纺车,寒冬深夜,嗡嗡的纺车声送我入梦。妈妈纺棉花的影子,至今常常在我记忆的荧屏上闪现。
纺棉花也叫纺线。木制的纺车,由一只大纺轮带动一支小锭杆儿。纺线时先要把棉花搓成油条似的布剂,捏在左手里,然后右手摇转纺车,把布剂从飞转的锭杆上引出线来,大约纺出多半尺长,绕在锭杆上,再纺。如此反复,锭杆上就绕出一个鸭蛋似的线棰儿,卸下来,放在瓦罐儿里。瓦罐儿里一般还放着鸡蛋,要轻拿轻放,不仅线棰儿抖搂不了,还能保护鸡蛋不被磕破,真是一举两得。纺线多是为了织布,但一般人家没有织布机,等线棰儿攒够一定数量,就和鸡蛋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儿零钱,打个油盐酱醋什么的也不作难了。过去,这是农村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
千百年来,我国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纺线织布也就成了农村妇女的主要劳动项目。正像古装黄梅戏里七仙女与董永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和现代评剧《刘巧儿》中唱的“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那样,男女分工合作,夫妻恩恩爱爱,生活虽苦心里也觉得甜。在德州地方戏中,乐陵哈哈腔有一出《摔纺车》的传统剧目,讲的是不务正业的刘二嘎,在外赌输了钱回家拿老婆出气,挨打挨骂老婆都忍了,可是摔坏了纺车,等同断绝了一家人的生路,老婆便忍无可忍地与刘二嘎大吵大闹起来。她发自肺腑的哭诉,终于使刘二嘎回心转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出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纺棉花在小农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难怪那时会有“家家纺车转,户户纺车声”了。
纺棉花不仅在小农经济中举足轻重,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几百架纺车在窑洞前一字儿摆开,男女八路军战士一齐动手,自己纺纱织布做军衣,挫败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当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坐在纺车前纺过棉花。如今,这一架架简单的土纺车,成了革命文物,放在博物馆里,吸引着无数后人景仰的目光。
旋锭杆
纺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就是锭杆,这部件又很爱坏,一架纺车往往要备用两三支,所以锭杆的需求量非常大,旋锭杆也就成了一个热门行业。
旋锭杆也叫铣锭杆。铣,这个现代工业的技术用语,大概就是从落后的手工业中学来的吧。锭杆是一尺来长,两头尖细,中间略粗并旋有凹槽儿的一个木轴儿,纺轮带动它转起来,才能纺出纱线。由于长期不断地旋转,尖细的两端很容易磨损,失去光滑而跳动不稳,必须换支新的。
旋锭杆的木料很讲究,质地松软的杨、柳、杉等不能用,最好是檀木、枣木、梨木也行,顶不济也得是槐木、榆木,只有木质坚实细腻,旋出的锭杆才光滑好使,经磨耐用。一支锭杆的价码,完全根据木料的好坏而定。如果谁家有一支檀木锭杆,简直成了宝贝,不用时摘下来包在棉花里,生怕碰坏了。有人来借纺车,这支锭杆一般是不会外借的。
旋锭杆的并非只旋锭杆,也旋擀面杖或捣蒜棰子,反正用一套工具,旋的都是木制品,技术操作也差不多,为了养家糊口,为什么能挣的钱不挣呢?
每到年节,他们还旋一些陀螺或冰尜,拿到集市上去卖。冰尜大的如蔓菁,小的如鸡蛋,有一头尖的,也有两头尖反倒都能转的,上面刻着图案或涂着颜色,在洁白的冰雪上旋转起来,美似一团绽放的花朵,很受孩子们的喜爱。抽冰尜要不断扬起手臂,跟着飞转的冰尜跑来跑去,是冬季进行户外活动,加强体育锻炼的好方法。如今旋锭杆当然没了市场,可是旋冰尜作为少年或老年人的健身器材,还是可以开发利用的。
吹鼓手
吹鼓手,现在也称吹奏班子或音乐队,受雇于红白喜事,在我区各县市普遍流行。一个班底有四至八人,主要乐器是唢呐,配以笙、笛、二胡、小锣小鼓等。一个好班子,不仅会演奏各种曲牌,还会唢呐卡戏或演唱。大户人家为了摆阔寻热闹,有时雇来两三套班子,相互竞技赛艺,引得围观者喝彩声不绝,煞是喜庆火爆。
按行规,吹鼓手和唱戏的是一家人,不论相识或不相识的,见面即称兄弟。剧团演职员在行军赶路时,如果听到村里有鼓乐声,赶了过去就被让到上座,会吹的吹,会唱的唱,即使是管服装道具的,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照样吃吃喝喝、混个酒足饭饱。
“文革”期间破四旧,吹鼓手被视为封建文化而遭禁,老百姓办红白喜事不能没动静,就支起大喇叭放录音。然而,吹鼓手的作用有些是大喇叭很难代替的。那时乡村用电尚不普及,没有电大喇叭不响,死气沉沉,喜事办得不喜庆。而办丧事,陪棂的人不能老跪在那里哭,吊唁的人来了要及时通知陪棂的人,吹鼓手在门外一吹号就行了,没有吹鼓手得安排专人通风报信,那人一不留神误了通报,没有人陪棂你说尴尬不尴
尬!
过去吹鼓手被视为下九流,新社会被称为民间艺人,社会地位提高了。乐陵市刘凤祥,从小随父当吹鼓手,练就一身本领,30岁应聘为沈阳音乐学院教师,“文革”中被赶回家,仍在民间从事演奏活动。他吹的唢呐优美动听,技艺超群,被群众誉为“吹破天”,成为县政协委员。他曾多次参加省市文艺会演,1980年代表德州晋京出席农民文艺会演,他的唢呐独奏《百凤朝阳》和卡戏河北梆子选段,获优秀节目奖,被拍摄成艺术片,他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刘凤祥从此名声大振,周围县市许多人都慕名前来邀请,出价比一般吹鼓手要高几倍。
我市过去有一位县文化局长,曾当过剧团团长,能唱几口河北梆子。县剧团解散后,几个艺人组成演奏队,邀请退休的老局长参加,老局长耐不得寂寞,应邀当了吹鼓手。许多老百姓认识他,见老局长来了,觉得很长脸,格外光彩,不仅开价特别高,而且老局长唱上两段之后,就赶紧把他请到上席,待为贵宾。你看,名人效应就是非同一般,不服不行。
杂耍
德州是杂技之乡。据宁津县有关史料记载,黄家镇杂技古会,每年八月十五至九月十五举行,省内外许多杂技班都来这里汇集,各种杂技道具也在这里出售,还可拜师学艺,选人组班,散会后各奔东西,走江湖,卖艺为生。仅这个县张鳌乡野竹李一村,就有近百个大小杂技班子,400多名杂耍艺人,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拿起家伙来,人人有一手。”
杂耍是杂技艺术中的基础项目,主要是手技、蹬技、顶技、口技、车技、踩技等,一个人即可撂地,几个人也能摆场,大小随意,行动便捷,演出机动灵活,这是德州最具传统特色的老行当。
杂耍艺人以一家一户为主,杂有亲朋或学徒。每到一地演出,条件好的围一圈布账,卖票,条件差的就地打个场子,演俩节目敛几个小钱。杂耍艺人一般都是多面手,能文能武,浑身功夫,几个人轮番上阵,大半天演出不会重样儿。当然,为了等待观众,拖延时间,演出前每每要说一阵闲话,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玩艺儿是假的,功夫儿是真的”等等,嚼来嚼去,磨得人耳朵眼里生茧子。为了迎合观众的好奇心和换得人们的同情,多赚几个钱,有些艺人不惜铤而走险,演出吞剑、大卸八块等残酷恐怖节目,有人不慎丧了性命。人们都说演出这种节目的孩子,不是父母亲生的,是偷来或拐骗来的,否则,哪有这样狠心的父母?其实,人们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旧社会杂耍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欺压凌辱,为了生计不得不赌上身家性命。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禁演了一批惑淫惑盗和血腥恐怖的节目,危害杂耍艺人身心健康的吞剑,大卸八块等也很快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创意新颖的优秀节目,如《快乐的炊事员》、《抢椅子》、《机器人》等等,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耍猴
在宁津县黄家镇杂技古会上,有许多买卖驯养小动物的,如猴子、狗熊、山羊、小狗……特别是有灵性的猴子,买上一只牵了去,走江湖,耍把戏,天南海北,漂洋过海,度过风雨人生。
耍猴的多为单身,也有带着老婆孩子的,在乡村集市或城镇广场打个园场,敲一阵锣,冲着围拢来的人作一圈箩圈揖,说一段“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之类的开场白,便开始耍猴了。有的猴子光身儿,有的猴子穿衣戴帽儿,一副人模狗样的,先给大家敬一圈儿礼,活蹦乱跳的,很是乖巧可爱。猴子表演的节目好坏与多少,全看主人驯化的功夫。有的猴子会钻火圈、骑羊、耍刀舞棍,还有的会扮作孙悟空或醉汉,时而憨态可掬,时而活泼无比,令人欢喜,更令孩子们雀跃。可是,过去贫穷落后,围观的人不少,给钱的人不多,特别是孩子们兜里没有一分钱,只好把吃剩的地瓜、窝头或花生什么的扔过去,给捧着铜锣的主人或猴子。不管收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又饿又馋的猴子也不敢动,必须交给主人,等着赏赐,否则,主人手中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
耍猴游动性很大,哪里年成好能赚钱就往哪里去,城市乡村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如果你打听一下,十有八九是我们的老乡。在旱、涝、蝗灾连年不绝的旧中国,常常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鲁北人出去耍猴,却也闯出一条生路。如今,国泰民安,生活富裕,德州人民进入新世纪,正信心百倍地奔向小康之路,谁还为乞讨几个小钱去耍猴呢?
拉洋片
上个世纪之初,中国就有了电影,可是解放前,电影事业发展缓慢,只有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里才能看到,广大城镇和乡村的人只是听说过。那时,到处流行着拉洋片的,有人说这和看电影差不多,不少人便信以为真,拉洋片的生意就很快红火起来。
拉洋片需要一只大木箱,里面装上可以转动的画片,木箱前面开几个园园的小窗孔,通过凸透镜观看里面一幅幅不断变动的画片。拉洋片的人站在木箱的一侧,一手操纵画片的提线或转柄,一手拉动串连着的锣鼓,在叮咚作响的鼓乐声中,唱着画片的内容。唱腔多为当地民歌小调,唱词也通俗易懂,如“往里瞧来往里看,唐僧取经上西天,师徒来到盘丝洞,一个个美女赛天仙……”画片的故事一般都适合孩子们观看,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岳母刺字》等。但为了吸引成年人,也有《尼姑偷和尚》、《大姑娘洗澡》等低级下流的东西。不过,那样的画片只有简单的一两张,摊主也不唱内容,常常有托儿悄悄地看,偷偷地笑,让那些光棍汉子心猿意马,经不住诱惑,不得不把钱掏出来。因为价钱较高,这样的画片孩子们一般是看不起的。
拉洋片也叫西洋镜,这名称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其实不然。如果是从国外传入的,拉洋片的人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大城市里,而恰恰相反,他们多数是来自乡村。据一份文化资料记载,当时活跃在上海滩的拉洋片的人,以山东的农民居首。他们所以给这种把戏加上个“洋”字,无非是以洋代土,掩人耳目,多挣几个钱罢了。人们乍开始看西洋镜,还有点好奇,而一旦看过电影,便觉得大相径庭,受骗上当了,因此创造出“拆穿西洋镜”这个俗语,表示骗局或阴谋被揭露和识破的意思。解放后,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谁还去看那被拆穿的西洋镜呢!
说唱艺人
我国传统的说唱艺术,现在统称曲艺。表演者一人至三五人不等,有的只说不唱,如评书;有的只唱不说,如河南坠子;有的又说又唱,如大鼓;有的不说也不唱,只有表演,如双簧。形式多种多样,演出简单方便,只要求一桌或一椅,一鼓或一弦,一般不需特意化妆,更无需舞台布景,场边地头、室内露天演出均可,说唱通俗易懂,普及华夏大地,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说唱艺术在德州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城德州地处京津门户,运河要道,津浦石德铁路在这里交汇,是一个发达繁荣的水陆码头,也是各路艺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这里的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把各种演唱艺术融留下来。据不完全统计,在德州市上演过的曲种有: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木板大鼓、胶东大鼓、乐亭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天津快板、天津时调、快板书、渔鼓坠、数来宝、单弦、相声、评词、皮影、双簧等;而现代曲艺大师也有不少人来德州演出过,如骆玉笙、马三立、侯宝霆、侯宝林、郭启儒、马季、马增芬、马增慧、高思培、高元均、范振玉、孙金枝、刘兰芳、郭文秋、杨立德、孙少臣、孙振业等。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德州这块群众文化艺术的沃土上,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说唱艺人,武城著名琴师谢其荣,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曾为白妞、黑妞弹弦伴奏,看过《老残游记》的人都记得,白妞在济南明湖居演唱梨花大鼓的火爆动人场面。谢其荣熟谙白妞、黑妞清脆婉转、刚柔相济的演唱风格,严格教练女儿谢大玉,使其造诣颇深,成为继白妞、黑妞之后的梨花大鼓的优秀传人、名声远播京津沪宁及东北等地。乐陵鼓书艺人左玉玺,父子叔侄、胞兄胞弟,都演唱西河大鼓,且不断革新,自成一格,被称为鼓书世家。抗战期间,左玉玺因拒绝为汉奸演唱,惨遭毒打而亡。其侄左金魁继承叔父的人生品格和唱演技艺,为避顽匪威逼,潜回家乡,建国后参加省曲艺会演,荣获演唱一等奖,并当选省曲协副主席。此外还有禹城的曲艺作家张军及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夏津山东大鼓演员王长志等。
解放前,说唱艺人多数是散兵游勇,以演唱糊口谋生,被称为“要饭的买卖”。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说唱艺人组织起来,我区各县市普遍建立了曲艺队、曲艺厅,曲艺事业得到迅猛发展。上世纪50年代,德州市曲艺队有固定演出场所五处;夏津县曲艺队一度发展到100多人;1982年宁津县举办曲艺训练班,招考学员,应试者多达1500余人。广大的曲艺工作者,被称为文艺轻骑兵,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不仅说唱优秀的传统曲目,而且积极创作现代曲目,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一车高粱米》、《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设精神文明,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相关人物
田毅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德州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