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纺织业发展史话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1716 |
| 颗粒名称: | 潍县纺织业发展史话 |
| 分类号: | K295.2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17-132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潍县纺织业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叶,那时,全县正进入宽幅织布机取代土纺土织的最盛期,潍县纺织业发展史话。 |
| 关键词: | 潍县 纺织业 发展 |
内容
潍县纺织业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叶,那时,全县正进入宽幅织布机取代土纺土织的最盛期。这个发源地更是“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抒声。”这里以往就有着“贫家绩麻纺线,裕户借机而织”的传统,历代对棉麻蚕桑的种植、纴缕丝帛的制作都有着光辉的一页。据有关史料考证,潍县桑丝之用,可溯之夏商,葛麻普及于秦汉,棉纺术亦不止兴自元代黄道婆之后,因晋书早有“布衣蔬食”的记载。就近代而言,手拉梭的使用是由这里首创;宽面织布机的引进,是由这里开始;20年代潍县印染业跃居华北之冠,为人民衣着起划时代的变化,乃是因为当地农村有6万大机为后盾;解放后的潍坊更是腾飞猛进,当前已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纺、织、印染的完整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轻纺基地之一。
男耕女织和女纺男织潍县像全国各地一样,在劳动人民中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男耕女织”的说法,曰“衣衾之供,悉自妇姬”,‘昔之妇女,皆手自纺线,以供缝织”,“乡民衣衾,悉赖自给,农妇从业,终年操持……”。可见早前这里纺线织布全是由妇女承担的。
过去的纺织,对妇女来说,是一项极端艰辛而需终年不停的劳动,全靠两手操作。据传最早的纺线是沿用绩麻方法,先将棉絮搓成条状,粗若手指,以木制丁字形纺槌拨转捻线。此说不见于经史,因我们的老祖先是以丝帛为衣。不知什么时代出现了纺车,这是纺线史上一巨大飞跃,有人说见书于宋元,恐不可靠,或许还该提前些,这里没有追考的必要。只知有了纺车,纺线效率大增,可能从此开始了穿棉布的新纪元。说利用纺车纺线功效大增,只不过与前相比而言,因为一手摇纺车,一手续棉絮,就是昼夜不停也纺不了多少,无怪乎为了蔽体,昔之妇女非“终年操持”不可了。花上一两年工夫,纺成足够的线才能上机而织。说起早前织布机的老样,年纪大的人一般会知道,也许有些珍惜家什的农户,至今还保留着这种遗物,不忍弃毁。原由是祖辈对这东西的购置太“来之不易”,是他们的传家宝。当时虽然家家需要织布,可不是每家有机,多半是借租他人之机。这种机的机体,是一色的硬坚木料,上面连个铁钉也找不到,构造笨重与否无可非议,可叹的是操作方式:用两足交替蹬动,使两组经线分别上下;用一手撩动线梭以织纬线,同时用另只手卡紧,左右交替,就这样一递一换,一来一往,一天能织多少,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就可想而知。但别以为这笨重的苦营生太原始,它乃是近百年之内的事儿。
纺线织布,又苦又累又慢,妇女“终年操持”仍难供家人所需,男人们不得不“在耕作之余,亦相协作”。常年忙于种田的男子汉,多半不太善纺,但浆线、刷机等活,由于力气大,则干起来比女人顺手,特别他们的天然大脚,蹬起机来要比小脚女人轻松自如得多。当着后来有人创造了手拉梭,效率猛增两倍,小脚女人若是整日蹬机,确也不堪其苦了。
这手拉梭的改进,应该说是一大了不起的发明。就用那么一条绳儿,挂于机上,下分两股,牵动着两个梭盘,一拉一松,便冲击布梭产生往返。其过程是:当吊绳一拉,牵动两梭盘内冲,便推动在一头的布梭射向对面;当绳一松,布梭的惯性又将对面那由于拉绳时已靠向内侧的梭盘冲回原位。当再次拉动吊绳时,布梭又返回这边。既简单,又有力,要比撩梭好上百倍。正是由手拉梭的应用使农村广大妇女,用不着再“终年操持”了。效率大幅度提高,自然意味着两脚蹬机速度加快,这确非小脚女人所能胜任,这就是女纺男织的起点。也正是由于这一改进使织布专业户一下子多了起来。于是史书中有了“男子从织,女子鬻布”的记载。
常年业织人家多另行挖地建棚,名为“地屋子”,大小一般容二三台机,深仅可使成年人站立,上顶向一边倾斜,前面开窗以透光亮。这种屋有许多优点,冬暖夏凉,更可保持一定的湿度。寒天不需生火炉取暖,无冰冻之虞;暑日则前后开通风口,可清除闷热。就是节日闲暇,人们也多愿集聚在这里聊天,成为惬意场所。购置木机,建地屋以常年织布,是为当时人们所十分羡慕的事。
社会上对业织户的产品,都有通用的规格,分小布、丈五弦子、三丈弦子等。他们的收入一般要高于普通种田人,很少有倒闭亏损之患,因为大多数常年业织户并不是弃农从织,只作为一项农家副业。不过购一张机,需相当资金,在那多数人家糠菜半年粮的社会,有的户几辈子也买不起,因之普及不是很快。至晚清时期,专业户又有所发展,“男耕女织”已完全为“女纺男织”所取代,故县志有“……妇女手自纺线……鬻之机工”的记载。
张瑞芝与潍县第一架宽面织布机手拉梭的出现,使台机日产量猛增两倍多,熟练机手可日产20余尺,从而大大推动了家庭织布的商品化生产,至清朝末年,专织户几乎已遍及所有农村,市场自然也就出现了竞争,这又使人们在品种花色上出点子、想办法,不久便有条纹布、花边布、格子布等问世了,这类新产品一出来就受到欢迎。往年所产土布皆是白色,必须经过染色,方能穿用。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习俗,常人不能着白色衣服。清贫人家有了白布只好再用槐树花、高粱糠等作为染料,以改变坯布本色。有了条格布,可直接应用于做单衣,省却一道印染工序。又各种宽窄不同的条纹,大小各异的格子,有着装饰作用,比穿青一色要美得多,因之很快畅销于城乡各地。这又启迪业织户向着改进布的款式迈步了。
清末民初,有人从日本引进了铁木织布机(简称铁机),可织幅宽为2.6尺的棉布。这种机被启用伊始就显示出其优越性:只消用两脚蹬动,即全机工作自如,比拉梭布机功效高而省力,产品质量更佳,于是淘汰旧机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对此我们不能不提一下本县第一个引进宽面铁机的人物——张瑞芝。
张瑞芝,字辑五,寒亭镇寒亭村人,出生于一个生活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敏颖悟,兼口齿伶俐,童年入塾,对先生所授只两遍即可背诵如流。家人见他有旷世才华,遂竭全力供他读书,果不负所望,在学校里连连跳级,20岁刚出头,便随同比他大四五岁的同学东渡去日本留学。他一到日本,就看到了人家那发达的工业,远非祖国可比,像衣着这件生活中的首要大事,在日本根本不需同中国那样,要以占半数的女人们为之终日操劳,只不过几家工厂即可供人民穿得那么华美。这太使他羡慕了,于是立志攻学染织专业,以期学成后回来为祖国振兴实业。
1907年,他征得家人同意,以卖掉部分家产的钱,由日本输入了6台铁木织布机,与张伯言等人一同试织宽幅棉布,并打算推广后开创东洋印染新法。这位带头人特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爱国布,其质地良好,较之土布光滑均匀,纹理紧密,被社会上称作“洋”布。他更用所学“新染色法”配料,人工试染各种色布,获得成功。
张瑞芝本想由此大力发展新型染织事业,但缺乏资金。乡人虽然看到了这种宽幅布的优点,然而思想守旧,对这种乍见的“洋玩意”前景怎样,疑虑重重,一时不敢盲目插手资助;在那一味闭关自守的清朝社会上层,更不想予以支持,致使他的这一创举,昙花一现,遂即夭折。他的后人张晓初,曾留有他所撰“关于发展新型染织”、“日本染色”等文稿,以及自制的各种颜色的染料标本、画册等遗物,后历经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地方杂牌军队骚扰等劫难,已一无所存了。
张君的新型染织业没有发展起来,究其社会原因,是清廷腐败,国人未觉醒的缘故。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担任过革命军某部军需职务,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今寒亭镇齐家埠村的龙王庙址前齐芾南的纪念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但军阀混战继起,相互割据。张瑞芝见到这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现实,对从政事意懒心交,遂去了苏联。抗日战争时期,由苏联转到新疆伊宁县,在那里重操旧业,打算奠定根基,东山再起,以实现其发展中国染织业大志。1942年曾发明过两种简易印染机器,登载于《新疆日报》。但当时依然得不到政府重视,虽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孤掌难鸣,资金周转不灵,后年事日高,事业作罢。
万张织布机本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已被摧垮,城乡固有经济体系动摇。自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潍县辟为商埠和胶济铁路早已通车等因,洋货突然大量渗入,冲击了当地自然经济。作为传统的土线土布,首先受到舶来品的威胁,对比之下土布相形见绌。外来棉纱物美价廉,上机方便,自然织布者多愿采用,所产的这种“洋线土布”,质量是比纯土线布提高了许多,但解决不了幅宽问题,仍难同外国布相抗争。至民国初年,“洋”布已充斥市场,土布产销每况愈下,于是织布机的改良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新式大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飞快的速度普及开来的。下面介绍几个继张瑞芝之后推广使用宽面织布机的有关人物和事件。
先是1910~1912年,城里人杨渭、郎瑞东、陈晋堂等人从外地购进了铁木结构织布机在北关设立博济织布厂,生产白、黑、灰平纹布,亦命名为爱国布,质地可与外国货媲美。但是,也不知是由于此厂设在业织户很少的城里的原因,还是别的缘故,其影响不大,甚至在农村很多人还不知本县有这么个能织宽幅布的厂家。
潍城东乡邓村胡玉瑶,祖祖辈辈以织布为业,到他这一辈看到当地土布获利微薄,甚感忧虑,自己是业织之家,不甘心坐等倒闭,乃得知我国东北三省已有铁机织布厂,便着他的长子去辽宁省营口学习新法,学成后便从那里买了几台铁机,带回家推广使用。胡不保守,曾在亲朋族间大力倡导使用,凡用者皆获厚利,这是民国初年的事。
前邓村还有个名叫胡曰汉的人,也是一个对发展新型织布业做出贡献的人物。此人从小聪明好学,善于思考,尤其爱好机器学,曾去哈尔滨俄国机器厂学徒,经过刻苦努力,竟当上了该厂的技师。他认为家乡土法织布必须改良,认定手工生产必将由机器来取代。民国建立后,他购买了日本产铁木机4台,回到家乡联络乡里王举才、董风偕等人使用这种新机生产。为了推广,还号召和资助邻里使用。他们的产品是真正的堪与外来品相比的国货,质地之优良为社会所公认,抵制外洋之举为社会所赞许,对其产品争相抢购。一传十,十传百,使用铁机就成了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条新径。
1920年滕虎忱在潍城创办了华丰机器厂,他看准当时社会上掀起的换铁机热潮,便对这种机进行仿造。此人对借鉴外来制品十分认真,仿造时一丝不苟,使得自己的产品无论式样还是性能,都与样品无所差别。用户大得实惠,声誉一经传出,纷纷认购,该厂遂批量生产。顿时,一场换机热、织布热席卷全县,遂蔓延到昌邑、安丘等县。潍城里以工厂命名的织布厂家也应运而生,较大者有德信亨、考振苦、聚祥永和县办平民织布厂等。它们不止生产平纹白布,而有斜纹、线呢、哔叽等档次。
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万张织布机”的美誉即由此而起。其实铁机数远不止一万张,而是日愈增多。以眉村、穆村为中心的潍河西岸,南起大岭、〓山、北到宋庄、寒亭、固堤(包括昌邑县200多个村庄)大有人人弃农就织之热,华丰机器厂生产的铁机,早已供不应求,因之又有了天丰、蚨丰、洪丰、新华等以生产织布机为主的铁工厂。据粗略统计,在1935年前后的极盛期,穆村、眉村一带有机两万台,寒亭、固堤一带也不下两万台,加上其它区和城里,共约6.5万台(所说大机台数,实际包括尚生产小布的木机在内),连上安丘、昌邑等县,号称“十万大机”,如此盛况,在全国来说恐怕亦不多见。
这里还需补叙一下以布匹花纱交易为主的眉村市集,当年曾倡导铁机、推广新法织布有声誉的胡曰汉、王举才等人,为了使产品销路畅通和便于线纱收购而联络各村知名人士,于1917年在眉村成立布线集市。曾一度成为全县最大最集中的纺织品集散地。每当一、六市集这天,布商、线贩,头天即云集而来,三里长的市街两旁,线、布堆成小山,人流潮水般拥挤。一集日布销售量达4.5万匹,线750件(每件100公斤),成交额常突破10万元银币,这在一般城市中也是少有的。
维护织布业者利益的两大事件潍县织布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下面介绍一下为伸张正义,维护织布业者利益和坚定立场,力排诽谤中伤的两件事件。
一、眉村方碑眉村方碑是潍县工农大众抗暴抗税斗争的历史见证。事件于1926年春发生在织布业最繁荣的南眉村,前后历时18个月,至1927年9月取得彻底胜利。这场斗争,迫使官府屈从民意,致令豪强低头敛迹。
当年潍县织布业的盛况,一到眉村市集,即可见一斑:72家饭馆,24处银号;大车小辆满载棉纱白布,川流不息,一个集日成交额常突破10万元银币。这不能不招致一些地方恶棍蓄意从中渔利。以潍县东关郝尧顺为首,纠集了乡间于梅、泮登科、杨道三等势力人物,买通了官府,打起“安(丘)、潍(县)、昌(邑)机税征收会”名义,刻图章,印税册。为制造声势,还扯起两杆大旗,在眉村集上开始“安税”。规定每张织布机先交一块银元领取税册,后按期纳税。对官字号,老百姓怎敢不遵,这使得郝、于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大头银元滚滚而来,一个集日竟收得6000多元,一连就是半月。他们白天敲诈勒索,夜宿烟馆妓院,尽情挥霍着织布人的汗水。一时人言啧啧,怨声载道,一场拒税抗暴的怒火在广大织布业者胸中燃烧起来。
这些收税者,虽然有官府,终是心中有鬼,特别这地方当年曾有过“与盐巡对抗,火烧盐店”的壮举,使之不敢过于蛮干,生怕惹起麻烦。他们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先安顿住地方上某些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物,方法自然是收买。说来也真有点戏剧性,他们弄巧成拙,自讨苦吃。在这里引出了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物——王景元。
王景元(1847—1929年),前眉村人,家中清贫,只读过一年半书,但有着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对事物反映敏捷准确。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一生专为穷人打不平,不畏权势。如有一次一个老乡被人诬陷盗马,在安徽省睢宁县吃官司,他代为出庭申辩,县官见他破衣滥缕,蓬头垢面,便道:“看你这副模样!”他当即回讥:“那我只好回家叫‘八弟’来!”这是骂县官的一句话,因这“八弟”是指《隋唐演义》中的罗成,意即“我来打官司,你却相女婿”。为此一事,乡里说他是“敢提着脑袋进衙门的硬汉”。
王景元这样人物,自然在地方上有些名气,郝尧顺一伙打算先买住他,便带了礼物去“拜访”。一进门就“慷慨”地给了王景元的小孙子5块大银元,留下礼物后向王示意:“初次来访,不成敬意,大头子还在后头。”王景元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对来人的礼物没有拒绝。郝等认为大事已妥,遂放心征税了。他们向织布户下令:“半月内领取税册,逾期严惩不贷”。但他们哪里知道王景元早已查访去了,及侦知是他们勾结官府为非作歹,当即愤怒地对乡亲说:“谁来收税,只管打东西,打死了抬到我家去!”人们虽然没有动手打那些征税者,可一下子无人缴税了。这还了得,“安潍昌机税征收会”马上请官府出面。本与他们沆瀣一气的潍县衙门,一听禀报有人拒税,火冒三丈,马上下令传讯抗缴机税的带头人。王景元本打算就去县衙听“审”,这时又跳出了另一个要为民除害,愿试试官府有何利害的年青人,他激情地说:“你,年纪大了,又不是织布户,这官司由我来顶着打好了,就舍一身剐干到底!”这个青年,就是至今当地尽人皆知的别号叫“老八路”的梁正中。
梁正中,前邓村人,曾在朱德部下当过红军战士,所以人称老八路,晚年在家从医。他的后人都一直从事革命工作,是当地一个十分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庭。当初梁正中出面打这场官司还不到20岁。
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较量,一方是郝尧顺为首的有财有势的强梁豪绅,他们仰仗的是官府大人;一方是以梁正中为首的织布业户代表,他们的后盾是工农大众。从1926年春开始,时断时续。“税会”一方,本属倒行逆施,但有县太老爷撑腰,自是强词夺理,耍尽花招,以冀保住他们的“安税合法”。说什么织布户自产自销,没有管辖,常常尺码不足,弄虚作假,坑害买主;安税是为配合商团,管理市场,监督制造等。群众则知道对布业收税,不是来自省城京都的正当条款,全是他们假公济私,巧立名目。既然官司打起来了,不弄个水落石出,就决不罢休。相持局面一年多,胜负未分。王景元再也忍不住了,决心越级上告,遂叫着梁正中到省城济南递了状纸。他们代表着安丘、潍县、昌邑3县的织布户,也使省府知道来者不善,终不敢徇私枉法,最后判:无故课税、官逼民反。并立令将该税会取缔,追还所索税款。
胜利了,工农大众胜利了,连唱了12天大戏以兹庆贺。为纪念这正义而伟大的斗争事件,特于1927年9月在眉村街关帝庙前立一方碑,由文人孙正梓、王乐浩撰写碑文,将此事件前后经过,刻于碑上。碑文特别指明,农民自产棉布,一律不缴税。同时也为了杜绝短尺少码情事,碑上书有标准尺码,并将尺、寸的具体长度,刻在了碑座上。后凡有因布的尺寸问题引起争端者,即前来辩别是非,卖方买方两相无亏,民心大悦,正是这座方碑的正面那4个大字所指,“惠及工商”。
二、函文诽谤无所惧,伸张正义驳谣言潍县织布业盛期,年总产量高达六七百万匹,远销河南、甘肃、陕西、内蒙、山西、安徽、江西、四川等十几个省区。据《潍县志稿》对民国20年(1931年)统计,全年光由火车站运往外地的布匹达3600吨,使得大半个中国的百姓能穿用我潍县所织的棉布。潍县劳动人民有这么大的贡献,理应享有崇高荣誉和受到鼓励与支持,然而在那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社会,不但得不到任何外来协助支援,反而屡屡招来许多麻烦,妒嫉、指责以至诬陷、破坏。最典型的当属南昌市商会通过江西省国民党部这样上层机构而成文的一次诬陷。他们以“抵制日本,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由,责难潍县织布主竟用日本产纱线,诬陷潍县工厂勾结日本,以日货冒充自己的产品;说潍县布业是“为虎作伥”,要协助日本“以冀打倒中国内地一切手工业”。他们函告济南商会,对此事查询答复。甚至在文中提出对我地布业要“严为取缔”字样。这确是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因为在当时尽管上层不乏与日本明来暗去之事,但双方名义上是仇敌,若有谁胆敢公开做出有利于日本的事,会被斥为汉奸。济南商会并不是不知潍县当时织布的情况,对江西省的责难诬陷,有理由直接驳回,但虑于这是通过该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来的函件,不免小心翼翼,怕在某些小节上被人抓住把柄,终不敢理直气壮地回复,还是着潍县处理。面对江西省来函,究竟如何办,也给当时的潍县工商界当权人士出了一个难题。
赣省说潍县布业所用的棉纱“悉供自仇方”,并不是凭空捏造;说潍县将日本产品“改头换面”冒充国货推销则纯属诬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潍县织布业方兴未艾,靠当地农村手工纺线,早已不能自给,不得不依靠外埠,外购的纱线,既有国货,也有“洋”货。国内主要有青岛的华新、济南的鲁丰、上海的永安和无锡的振兴等厂的产品。不过远远不足所需,而大部需用外纱,外纱又多为日本在青岛、上海开设的纱厂所产,主要有富士厂的银月、新五星、长崎厂的宝来,隆兴厂的宝船,大康厂的金货,钟渊厂的花蝶、童鱼、宫女等牌号,潍县所用棉纱有80%是来自他们。面对这一现实,当地工商界人士认为,在国纱的的确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敌方在我国土地上办厂所产线纱,自己来织布,当无可非议。断不能以用仇方产品为由而扼杀这蒸蒸日上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兴事物。再说并没有用日货冒充国货的事,更绝无“为虎作伥”、“以冀打倒我内地一切人工手织品”的卖国行径。相反,振兴自己的织布业也正有利于抵制外货渗入。于是潍县工商界毫未示弱,而是为维护声誉,坚持真理,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部江西省执委会的来函。
织布乡首诞机器漂染厂本来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民族工业在资本主义刺激下已经萌芽,只是由于列强的控制压榨发展十分缓慢。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我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喘息机会,加快了发展步伐。机械工业的兴起,促使某些传统的手工业破产,也推动了某些手工业的前进,民间纺织便是最为显著的一例。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振兴实业是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学外国、办工厂风气在各大中城市逐渐展开。潍县本来占有重要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又兼早已辟为商埠,具有发展新工业的优越条件;当时城乡织布又正进入盛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30年潍县城里诞生了山东省第一家机械漂染厂——大华染厂。这是本县继华丰为代表的机器铁工厂之后又崛起的另一大新型工厂工业。这家染厂投产当年即大发其财,年终结算竟获利两万余元,产品蜚声省内外。不消说,使得仿效者立即接踵而来,由于耗资巨大,办厂不易,多用股份集资的形式合办。仅短短3年时间,这种大型染厂已发展到了7家,无论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跃居华北之冠。潍县的这一新生工业发展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县城的周围有着5万台织布大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这第一家染厂的创建和当时印染盛况,因为是它们促使了织布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全县织布机高达6.5万台,进入全盛时期。
大华印染厂的主要奠基人是张干臣(1894~1952年)先生,寒亭镇人。他求学时代即看到邻国日本经济发达,国家强盛,我伟大中华反受人欺凌,及知工业落后是重要原因,乃决心学习外国经验,振兴实业。后得到他的表兄于均生的赞助,留学日本攻读化工印染专业,并相约学成回国携手共创大业。张干臣勤学三载,回国后曾谋得山东济南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职务,1925年与潍县同乡郭立平等人在该校附设化工印染实习工厂,张亲自指导新法印染技术。当时他们得到潍县德信亨织布厂的支持,供应坯布以做试验,另一周村丝织厂也委托试染丝绸。经过反复试验,白布、丝绸之化工印染新法皆获成功。周村丝绸厂见功业告成,愿以高薪聘张、郭等人去周村开办丝绸染厂。张干臣想到当年受表兄于均生资助留学日本,曾有“学成回国,共同振兴实业”之约,再则又看到潍县织布业方兴未艾,开办染厂,前景无限,便毅然返回故乡与于均生共商集资办厂事宜。1928年适青岛有人也办染厂,从日本购进全套设备,但多次试车失败,遂忍痛出卖。张干臣获悉,与郭立平去青岛察看,凭所学分析检查,知机器质量无疵,该厂失败系技术不高所致,有如此现成的全套设备不出国即可买到,既省钱又省事,当即决定买下,经洽商以1.2万元成交。张干臣买到了机器,又以于均生为主集资3万元,在潍城东关购地建厂。在安装过程中,张、郭他们常亲自动手,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历时一年,基本就绪,于193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正式试车,一举成功。产品附以鲜艳夺目的彩色牌号,有“三顾茅庐”、“越国大夫”、“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等,国货胜洋货,物美价廉,深受社会欢迎,很快誉满南北,畅销于全国各地。
大华染厂的建立,为潍县机器印染创立了新纪元,一些大亨、富商以至权势人物,瞅准时机,争相集资兴办,相继建立的厂家有元聚、信丰、德聚、大丰、隆丰、利丰,共是7家,成为华北最著名的机械印染基地。其中尤以信丰规模最大,产量最高,技术力量最强,资金最为雄厚,日产色布达500匹,产品有各种阴丹士林色布,爱国色布,线哔叽、印花布、法兰绒、打连绒等。该厂还为自己的产品大作广告,除标明产品种类、质量,并贯串了“振兴民族实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内容,深得社会支持和外埠商客的光顾。
机器印染比土法染色本已高出百倍,各厂家出于竞争需要,又各自精益求精。尤其对各种阴丹士林色布,其色泽之美,质地之精,可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使社会上一时兴起了穿阴丹士林热。男女皆可,雅俗咸宜。青年男儿着件士林长衫,则显得潇洒庄重,落落大方;小姐少妇穿件士林旗袍,则越发秀丽妩媚,娴静文雅。就是在那当时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农村,姑娘、媳妇们也都喜欢做上一身士林裤褂,穿起来会格外露出她们的俊俏、端庄、朴素。可以确切地说,新法印染的出现,改变了这里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穿着青衣粗布的习俗。这一业绩,当归功于积极创办印染业的人们,特别是带头人张干臣先生;若归根结底,又是因为这里有着坚实的织布基础,新型印染才首先在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县城中兴起。
潍县印染,誉满全国,其所用坯布完全由当地农村供给,这无形中提高了原白布的声誉,甚至在外地有些染厂其产品质量不高,也认为是坯布不良的原因。因而凡属潍县织的布,就成了各省市的抢手货,布商不远千里来收购、定购。织布户从无滞销积压之患,远销21个省70多个大城市,从中可窥见当时盛况。
潍县织布本是历代相传,铁机虽属更新换代,但仍是家庭手工业范畴,后人易于继承;当地有多家新兴机器铁工厂,盛产织布机,随时可买可修;这里靠近线纱基地青岛,原料充足;产品声誉在外,销路畅通,无倒闭之患,无滞销之忧;这么多的有利条件,自然会日趋繁荣。农民购机织布热潮,越来越高,至1936年进入鼎盛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1938年1月9日,日寇铁蹄踏进了潍城,农村遂即全部沦陷,所有织布户不得不销声匿迹。在日寇、汉奸的蹂躏下,织布机被大量破坏,加上地方杂牌军蜂起,各据一方,扩充势力,他们自办工厂制造枪炮弹雷,但农村中并无钢铁,大机上的铁制机件就成了搜刮抢夺的对象。十几年的劫难,偷偷保存下来的已经寥寥无几了。
1945年八路军解放了潍县部分农村,人民政府号召解放区人民生产自救,幸存下来的织布机才又开始转动。1948年4月潍县全境解放,广大织布业者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纷操旧业。他们将被毁坏的大机残骸,以拼凑、修理、代用等方法使之再生。不几年,隆隆织布声又到处可闻了,走在最前面的依然是潍河两岸。
解放后的潍县划为潍坊市,在党的领导下这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大进军中,纺织业、印染业又曾是首先腾飞。棉纺、棉织、化纤、印染、毛纺织、针织等门类,一一跨入先进行列。被列为全国重要纺织生产基地。
(潍坊市寒亭区政协供稿)
男耕女织和女纺男织潍县像全国各地一样,在劳动人民中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男耕女织”的说法,曰“衣衾之供,悉自妇姬”,‘昔之妇女,皆手自纺线,以供缝织”,“乡民衣衾,悉赖自给,农妇从业,终年操持……”。可见早前这里纺线织布全是由妇女承担的。
过去的纺织,对妇女来说,是一项极端艰辛而需终年不停的劳动,全靠两手操作。据传最早的纺线是沿用绩麻方法,先将棉絮搓成条状,粗若手指,以木制丁字形纺槌拨转捻线。此说不见于经史,因我们的老祖先是以丝帛为衣。不知什么时代出现了纺车,这是纺线史上一巨大飞跃,有人说见书于宋元,恐不可靠,或许还该提前些,这里没有追考的必要。只知有了纺车,纺线效率大增,可能从此开始了穿棉布的新纪元。说利用纺车纺线功效大增,只不过与前相比而言,因为一手摇纺车,一手续棉絮,就是昼夜不停也纺不了多少,无怪乎为了蔽体,昔之妇女非“终年操持”不可了。花上一两年工夫,纺成足够的线才能上机而织。说起早前织布机的老样,年纪大的人一般会知道,也许有些珍惜家什的农户,至今还保留着这种遗物,不忍弃毁。原由是祖辈对这东西的购置太“来之不易”,是他们的传家宝。当时虽然家家需要织布,可不是每家有机,多半是借租他人之机。这种机的机体,是一色的硬坚木料,上面连个铁钉也找不到,构造笨重与否无可非议,可叹的是操作方式:用两足交替蹬动,使两组经线分别上下;用一手撩动线梭以织纬线,同时用另只手卡紧,左右交替,就这样一递一换,一来一往,一天能织多少,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就可想而知。但别以为这笨重的苦营生太原始,它乃是近百年之内的事儿。
纺线织布,又苦又累又慢,妇女“终年操持”仍难供家人所需,男人们不得不“在耕作之余,亦相协作”。常年忙于种田的男子汉,多半不太善纺,但浆线、刷机等活,由于力气大,则干起来比女人顺手,特别他们的天然大脚,蹬起机来要比小脚女人轻松自如得多。当着后来有人创造了手拉梭,效率猛增两倍,小脚女人若是整日蹬机,确也不堪其苦了。
这手拉梭的改进,应该说是一大了不起的发明。就用那么一条绳儿,挂于机上,下分两股,牵动着两个梭盘,一拉一松,便冲击布梭产生往返。其过程是:当吊绳一拉,牵动两梭盘内冲,便推动在一头的布梭射向对面;当绳一松,布梭的惯性又将对面那由于拉绳时已靠向内侧的梭盘冲回原位。当再次拉动吊绳时,布梭又返回这边。既简单,又有力,要比撩梭好上百倍。正是由手拉梭的应用使农村广大妇女,用不着再“终年操持”了。效率大幅度提高,自然意味着两脚蹬机速度加快,这确非小脚女人所能胜任,这就是女纺男织的起点。也正是由于这一改进使织布专业户一下子多了起来。于是史书中有了“男子从织,女子鬻布”的记载。
常年业织人家多另行挖地建棚,名为“地屋子”,大小一般容二三台机,深仅可使成年人站立,上顶向一边倾斜,前面开窗以透光亮。这种屋有许多优点,冬暖夏凉,更可保持一定的湿度。寒天不需生火炉取暖,无冰冻之虞;暑日则前后开通风口,可清除闷热。就是节日闲暇,人们也多愿集聚在这里聊天,成为惬意场所。购置木机,建地屋以常年织布,是为当时人们所十分羡慕的事。
社会上对业织户的产品,都有通用的规格,分小布、丈五弦子、三丈弦子等。他们的收入一般要高于普通种田人,很少有倒闭亏损之患,因为大多数常年业织户并不是弃农从织,只作为一项农家副业。不过购一张机,需相当资金,在那多数人家糠菜半年粮的社会,有的户几辈子也买不起,因之普及不是很快。至晚清时期,专业户又有所发展,“男耕女织”已完全为“女纺男织”所取代,故县志有“……妇女手自纺线……鬻之机工”的记载。
张瑞芝与潍县第一架宽面织布机手拉梭的出现,使台机日产量猛增两倍多,熟练机手可日产20余尺,从而大大推动了家庭织布的商品化生产,至清朝末年,专织户几乎已遍及所有农村,市场自然也就出现了竞争,这又使人们在品种花色上出点子、想办法,不久便有条纹布、花边布、格子布等问世了,这类新产品一出来就受到欢迎。往年所产土布皆是白色,必须经过染色,方能穿用。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习俗,常人不能着白色衣服。清贫人家有了白布只好再用槐树花、高粱糠等作为染料,以改变坯布本色。有了条格布,可直接应用于做单衣,省却一道印染工序。又各种宽窄不同的条纹,大小各异的格子,有着装饰作用,比穿青一色要美得多,因之很快畅销于城乡各地。这又启迪业织户向着改进布的款式迈步了。
清末民初,有人从日本引进了铁木织布机(简称铁机),可织幅宽为2.6尺的棉布。这种机被启用伊始就显示出其优越性:只消用两脚蹬动,即全机工作自如,比拉梭布机功效高而省力,产品质量更佳,于是淘汰旧机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对此我们不能不提一下本县第一个引进宽面铁机的人物——张瑞芝。
张瑞芝,字辑五,寒亭镇寒亭村人,出生于一个生活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敏颖悟,兼口齿伶俐,童年入塾,对先生所授只两遍即可背诵如流。家人见他有旷世才华,遂竭全力供他读书,果不负所望,在学校里连连跳级,20岁刚出头,便随同比他大四五岁的同学东渡去日本留学。他一到日本,就看到了人家那发达的工业,远非祖国可比,像衣着这件生活中的首要大事,在日本根本不需同中国那样,要以占半数的女人们为之终日操劳,只不过几家工厂即可供人民穿得那么华美。这太使他羡慕了,于是立志攻学染织专业,以期学成后回来为祖国振兴实业。
1907年,他征得家人同意,以卖掉部分家产的钱,由日本输入了6台铁木织布机,与张伯言等人一同试织宽幅棉布,并打算推广后开创东洋印染新法。这位带头人特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爱国布,其质地良好,较之土布光滑均匀,纹理紧密,被社会上称作“洋”布。他更用所学“新染色法”配料,人工试染各种色布,获得成功。
张瑞芝本想由此大力发展新型染织事业,但缺乏资金。乡人虽然看到了这种宽幅布的优点,然而思想守旧,对这种乍见的“洋玩意”前景怎样,疑虑重重,一时不敢盲目插手资助;在那一味闭关自守的清朝社会上层,更不想予以支持,致使他的这一创举,昙花一现,遂即夭折。他的后人张晓初,曾留有他所撰“关于发展新型染织”、“日本染色”等文稿,以及自制的各种颜色的染料标本、画册等遗物,后历经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地方杂牌军队骚扰等劫难,已一无所存了。
张君的新型染织业没有发展起来,究其社会原因,是清廷腐败,国人未觉醒的缘故。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担任过革命军某部军需职务,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今寒亭镇齐家埠村的龙王庙址前齐芾南的纪念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但军阀混战继起,相互割据。张瑞芝见到这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现实,对从政事意懒心交,遂去了苏联。抗日战争时期,由苏联转到新疆伊宁县,在那里重操旧业,打算奠定根基,东山再起,以实现其发展中国染织业大志。1942年曾发明过两种简易印染机器,登载于《新疆日报》。但当时依然得不到政府重视,虽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孤掌难鸣,资金周转不灵,后年事日高,事业作罢。
万张织布机本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已被摧垮,城乡固有经济体系动摇。自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潍县辟为商埠和胶济铁路早已通车等因,洋货突然大量渗入,冲击了当地自然经济。作为传统的土线土布,首先受到舶来品的威胁,对比之下土布相形见绌。外来棉纱物美价廉,上机方便,自然织布者多愿采用,所产的这种“洋线土布”,质量是比纯土线布提高了许多,但解决不了幅宽问题,仍难同外国布相抗争。至民国初年,“洋”布已充斥市场,土布产销每况愈下,于是织布机的改良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新式大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飞快的速度普及开来的。下面介绍几个继张瑞芝之后推广使用宽面织布机的有关人物和事件。
先是1910~1912年,城里人杨渭、郎瑞东、陈晋堂等人从外地购进了铁木结构织布机在北关设立博济织布厂,生产白、黑、灰平纹布,亦命名为爱国布,质地可与外国货媲美。但是,也不知是由于此厂设在业织户很少的城里的原因,还是别的缘故,其影响不大,甚至在农村很多人还不知本县有这么个能织宽幅布的厂家。
潍城东乡邓村胡玉瑶,祖祖辈辈以织布为业,到他这一辈看到当地土布获利微薄,甚感忧虑,自己是业织之家,不甘心坐等倒闭,乃得知我国东北三省已有铁机织布厂,便着他的长子去辽宁省营口学习新法,学成后便从那里买了几台铁机,带回家推广使用。胡不保守,曾在亲朋族间大力倡导使用,凡用者皆获厚利,这是民国初年的事。
前邓村还有个名叫胡曰汉的人,也是一个对发展新型织布业做出贡献的人物。此人从小聪明好学,善于思考,尤其爱好机器学,曾去哈尔滨俄国机器厂学徒,经过刻苦努力,竟当上了该厂的技师。他认为家乡土法织布必须改良,认定手工生产必将由机器来取代。民国建立后,他购买了日本产铁木机4台,回到家乡联络乡里王举才、董风偕等人使用这种新机生产。为了推广,还号召和资助邻里使用。他们的产品是真正的堪与外来品相比的国货,质地之优良为社会所公认,抵制外洋之举为社会所赞许,对其产品争相抢购。一传十,十传百,使用铁机就成了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条新径。
1920年滕虎忱在潍城创办了华丰机器厂,他看准当时社会上掀起的换铁机热潮,便对这种机进行仿造。此人对借鉴外来制品十分认真,仿造时一丝不苟,使得自己的产品无论式样还是性能,都与样品无所差别。用户大得实惠,声誉一经传出,纷纷认购,该厂遂批量生产。顿时,一场换机热、织布热席卷全县,遂蔓延到昌邑、安丘等县。潍城里以工厂命名的织布厂家也应运而生,较大者有德信亨、考振苦、聚祥永和县办平民织布厂等。它们不止生产平纹白布,而有斜纹、线呢、哔叽等档次。
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万张织布机”的美誉即由此而起。其实铁机数远不止一万张,而是日愈增多。以眉村、穆村为中心的潍河西岸,南起大岭、〓山、北到宋庄、寒亭、固堤(包括昌邑县200多个村庄)大有人人弃农就织之热,华丰机器厂生产的铁机,早已供不应求,因之又有了天丰、蚨丰、洪丰、新华等以生产织布机为主的铁工厂。据粗略统计,在1935年前后的极盛期,穆村、眉村一带有机两万台,寒亭、固堤一带也不下两万台,加上其它区和城里,共约6.5万台(所说大机台数,实际包括尚生产小布的木机在内),连上安丘、昌邑等县,号称“十万大机”,如此盛况,在全国来说恐怕亦不多见。
这里还需补叙一下以布匹花纱交易为主的眉村市集,当年曾倡导铁机、推广新法织布有声誉的胡曰汉、王举才等人,为了使产品销路畅通和便于线纱收购而联络各村知名人士,于1917年在眉村成立布线集市。曾一度成为全县最大最集中的纺织品集散地。每当一、六市集这天,布商、线贩,头天即云集而来,三里长的市街两旁,线、布堆成小山,人流潮水般拥挤。一集日布销售量达4.5万匹,线750件(每件100公斤),成交额常突破10万元银币,这在一般城市中也是少有的。
维护织布业者利益的两大事件潍县织布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下面介绍一下为伸张正义,维护织布业者利益和坚定立场,力排诽谤中伤的两件事件。
一、眉村方碑眉村方碑是潍县工农大众抗暴抗税斗争的历史见证。事件于1926年春发生在织布业最繁荣的南眉村,前后历时18个月,至1927年9月取得彻底胜利。这场斗争,迫使官府屈从民意,致令豪强低头敛迹。
当年潍县织布业的盛况,一到眉村市集,即可见一斑:72家饭馆,24处银号;大车小辆满载棉纱白布,川流不息,一个集日成交额常突破10万元银币。这不能不招致一些地方恶棍蓄意从中渔利。以潍县东关郝尧顺为首,纠集了乡间于梅、泮登科、杨道三等势力人物,买通了官府,打起“安(丘)、潍(县)、昌(邑)机税征收会”名义,刻图章,印税册。为制造声势,还扯起两杆大旗,在眉村集上开始“安税”。规定每张织布机先交一块银元领取税册,后按期纳税。对官字号,老百姓怎敢不遵,这使得郝、于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大头银元滚滚而来,一个集日竟收得6000多元,一连就是半月。他们白天敲诈勒索,夜宿烟馆妓院,尽情挥霍着织布人的汗水。一时人言啧啧,怨声载道,一场拒税抗暴的怒火在广大织布业者胸中燃烧起来。
这些收税者,虽然有官府,终是心中有鬼,特别这地方当年曾有过“与盐巡对抗,火烧盐店”的壮举,使之不敢过于蛮干,生怕惹起麻烦。他们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先安顿住地方上某些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物,方法自然是收买。说来也真有点戏剧性,他们弄巧成拙,自讨苦吃。在这里引出了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物——王景元。
王景元(1847—1929年),前眉村人,家中清贫,只读过一年半书,但有着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对事物反映敏捷准确。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一生专为穷人打不平,不畏权势。如有一次一个老乡被人诬陷盗马,在安徽省睢宁县吃官司,他代为出庭申辩,县官见他破衣滥缕,蓬头垢面,便道:“看你这副模样!”他当即回讥:“那我只好回家叫‘八弟’来!”这是骂县官的一句话,因这“八弟”是指《隋唐演义》中的罗成,意即“我来打官司,你却相女婿”。为此一事,乡里说他是“敢提着脑袋进衙门的硬汉”。
王景元这样人物,自然在地方上有些名气,郝尧顺一伙打算先买住他,便带了礼物去“拜访”。一进门就“慷慨”地给了王景元的小孙子5块大银元,留下礼物后向王示意:“初次来访,不成敬意,大头子还在后头。”王景元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对来人的礼物没有拒绝。郝等认为大事已妥,遂放心征税了。他们向织布户下令:“半月内领取税册,逾期严惩不贷”。但他们哪里知道王景元早已查访去了,及侦知是他们勾结官府为非作歹,当即愤怒地对乡亲说:“谁来收税,只管打东西,打死了抬到我家去!”人们虽然没有动手打那些征税者,可一下子无人缴税了。这还了得,“安潍昌机税征收会”马上请官府出面。本与他们沆瀣一气的潍县衙门,一听禀报有人拒税,火冒三丈,马上下令传讯抗缴机税的带头人。王景元本打算就去县衙听“审”,这时又跳出了另一个要为民除害,愿试试官府有何利害的年青人,他激情地说:“你,年纪大了,又不是织布户,这官司由我来顶着打好了,就舍一身剐干到底!”这个青年,就是至今当地尽人皆知的别号叫“老八路”的梁正中。
梁正中,前邓村人,曾在朱德部下当过红军战士,所以人称老八路,晚年在家从医。他的后人都一直从事革命工作,是当地一个十分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庭。当初梁正中出面打这场官司还不到20岁。
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较量,一方是郝尧顺为首的有财有势的强梁豪绅,他们仰仗的是官府大人;一方是以梁正中为首的织布业户代表,他们的后盾是工农大众。从1926年春开始,时断时续。“税会”一方,本属倒行逆施,但有县太老爷撑腰,自是强词夺理,耍尽花招,以冀保住他们的“安税合法”。说什么织布户自产自销,没有管辖,常常尺码不足,弄虚作假,坑害买主;安税是为配合商团,管理市场,监督制造等。群众则知道对布业收税,不是来自省城京都的正当条款,全是他们假公济私,巧立名目。既然官司打起来了,不弄个水落石出,就决不罢休。相持局面一年多,胜负未分。王景元再也忍不住了,决心越级上告,遂叫着梁正中到省城济南递了状纸。他们代表着安丘、潍县、昌邑3县的织布户,也使省府知道来者不善,终不敢徇私枉法,最后判:无故课税、官逼民反。并立令将该税会取缔,追还所索税款。
胜利了,工农大众胜利了,连唱了12天大戏以兹庆贺。为纪念这正义而伟大的斗争事件,特于1927年9月在眉村街关帝庙前立一方碑,由文人孙正梓、王乐浩撰写碑文,将此事件前后经过,刻于碑上。碑文特别指明,农民自产棉布,一律不缴税。同时也为了杜绝短尺少码情事,碑上书有标准尺码,并将尺、寸的具体长度,刻在了碑座上。后凡有因布的尺寸问题引起争端者,即前来辩别是非,卖方买方两相无亏,民心大悦,正是这座方碑的正面那4个大字所指,“惠及工商”。
二、函文诽谤无所惧,伸张正义驳谣言潍县织布业盛期,年总产量高达六七百万匹,远销河南、甘肃、陕西、内蒙、山西、安徽、江西、四川等十几个省区。据《潍县志稿》对民国20年(1931年)统计,全年光由火车站运往外地的布匹达3600吨,使得大半个中国的百姓能穿用我潍县所织的棉布。潍县劳动人民有这么大的贡献,理应享有崇高荣誉和受到鼓励与支持,然而在那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社会,不但得不到任何外来协助支援,反而屡屡招来许多麻烦,妒嫉、指责以至诬陷、破坏。最典型的当属南昌市商会通过江西省国民党部这样上层机构而成文的一次诬陷。他们以“抵制日本,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由,责难潍县织布主竟用日本产纱线,诬陷潍县工厂勾结日本,以日货冒充自己的产品;说潍县布业是“为虎作伥”,要协助日本“以冀打倒中国内地一切手工业”。他们函告济南商会,对此事查询答复。甚至在文中提出对我地布业要“严为取缔”字样。这确是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因为在当时尽管上层不乏与日本明来暗去之事,但双方名义上是仇敌,若有谁胆敢公开做出有利于日本的事,会被斥为汉奸。济南商会并不是不知潍县当时织布的情况,对江西省的责难诬陷,有理由直接驳回,但虑于这是通过该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来的函件,不免小心翼翼,怕在某些小节上被人抓住把柄,终不敢理直气壮地回复,还是着潍县处理。面对江西省来函,究竟如何办,也给当时的潍县工商界当权人士出了一个难题。
赣省说潍县布业所用的棉纱“悉供自仇方”,并不是凭空捏造;说潍县将日本产品“改头换面”冒充国货推销则纯属诬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潍县织布业方兴未艾,靠当地农村手工纺线,早已不能自给,不得不依靠外埠,外购的纱线,既有国货,也有“洋”货。国内主要有青岛的华新、济南的鲁丰、上海的永安和无锡的振兴等厂的产品。不过远远不足所需,而大部需用外纱,外纱又多为日本在青岛、上海开设的纱厂所产,主要有富士厂的银月、新五星、长崎厂的宝来,隆兴厂的宝船,大康厂的金货,钟渊厂的花蝶、童鱼、宫女等牌号,潍县所用棉纱有80%是来自他们。面对这一现实,当地工商界人士认为,在国纱的的确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敌方在我国土地上办厂所产线纱,自己来织布,当无可非议。断不能以用仇方产品为由而扼杀这蒸蒸日上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兴事物。再说并没有用日货冒充国货的事,更绝无“为虎作伥”、“以冀打倒我内地一切人工手织品”的卖国行径。相反,振兴自己的织布业也正有利于抵制外货渗入。于是潍县工商界毫未示弱,而是为维护声誉,坚持真理,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部江西省执委会的来函。
织布乡首诞机器漂染厂本来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民族工业在资本主义刺激下已经萌芽,只是由于列强的控制压榨发展十分缓慢。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我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喘息机会,加快了发展步伐。机械工业的兴起,促使某些传统的手工业破产,也推动了某些手工业的前进,民间纺织便是最为显著的一例。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振兴实业是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学外国、办工厂风气在各大中城市逐渐展开。潍县本来占有重要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又兼早已辟为商埠,具有发展新工业的优越条件;当时城乡织布又正进入盛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30年潍县城里诞生了山东省第一家机械漂染厂——大华染厂。这是本县继华丰为代表的机器铁工厂之后又崛起的另一大新型工厂工业。这家染厂投产当年即大发其财,年终结算竟获利两万余元,产品蜚声省内外。不消说,使得仿效者立即接踵而来,由于耗资巨大,办厂不易,多用股份集资的形式合办。仅短短3年时间,这种大型染厂已发展到了7家,无论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跃居华北之冠。潍县的这一新生工业发展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县城的周围有着5万台织布大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这第一家染厂的创建和当时印染盛况,因为是它们促使了织布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全县织布机高达6.5万台,进入全盛时期。
大华印染厂的主要奠基人是张干臣(1894~1952年)先生,寒亭镇人。他求学时代即看到邻国日本经济发达,国家强盛,我伟大中华反受人欺凌,及知工业落后是重要原因,乃决心学习外国经验,振兴实业。后得到他的表兄于均生的赞助,留学日本攻读化工印染专业,并相约学成回国携手共创大业。张干臣勤学三载,回国后曾谋得山东济南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职务,1925年与潍县同乡郭立平等人在该校附设化工印染实习工厂,张亲自指导新法印染技术。当时他们得到潍县德信亨织布厂的支持,供应坯布以做试验,另一周村丝织厂也委托试染丝绸。经过反复试验,白布、丝绸之化工印染新法皆获成功。周村丝绸厂见功业告成,愿以高薪聘张、郭等人去周村开办丝绸染厂。张干臣想到当年受表兄于均生资助留学日本,曾有“学成回国,共同振兴实业”之约,再则又看到潍县织布业方兴未艾,开办染厂,前景无限,便毅然返回故乡与于均生共商集资办厂事宜。1928年适青岛有人也办染厂,从日本购进全套设备,但多次试车失败,遂忍痛出卖。张干臣获悉,与郭立平去青岛察看,凭所学分析检查,知机器质量无疵,该厂失败系技术不高所致,有如此现成的全套设备不出国即可买到,既省钱又省事,当即决定买下,经洽商以1.2万元成交。张干臣买到了机器,又以于均生为主集资3万元,在潍城东关购地建厂。在安装过程中,张、郭他们常亲自动手,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历时一年,基本就绪,于193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正式试车,一举成功。产品附以鲜艳夺目的彩色牌号,有“三顾茅庐”、“越国大夫”、“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等,国货胜洋货,物美价廉,深受社会欢迎,很快誉满南北,畅销于全国各地。
大华染厂的建立,为潍县机器印染创立了新纪元,一些大亨、富商以至权势人物,瞅准时机,争相集资兴办,相继建立的厂家有元聚、信丰、德聚、大丰、隆丰、利丰,共是7家,成为华北最著名的机械印染基地。其中尤以信丰规模最大,产量最高,技术力量最强,资金最为雄厚,日产色布达500匹,产品有各种阴丹士林色布,爱国色布,线哔叽、印花布、法兰绒、打连绒等。该厂还为自己的产品大作广告,除标明产品种类、质量,并贯串了“振兴民族实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内容,深得社会支持和外埠商客的光顾。
机器印染比土法染色本已高出百倍,各厂家出于竞争需要,又各自精益求精。尤其对各种阴丹士林色布,其色泽之美,质地之精,可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使社会上一时兴起了穿阴丹士林热。男女皆可,雅俗咸宜。青年男儿着件士林长衫,则显得潇洒庄重,落落大方;小姐少妇穿件士林旗袍,则越发秀丽妩媚,娴静文雅。就是在那当时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农村,姑娘、媳妇们也都喜欢做上一身士林裤褂,穿起来会格外露出她们的俊俏、端庄、朴素。可以确切地说,新法印染的出现,改变了这里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穿着青衣粗布的习俗。这一业绩,当归功于积极创办印染业的人们,特别是带头人张干臣先生;若归根结底,又是因为这里有着坚实的织布基础,新型印染才首先在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县城中兴起。
潍县印染,誉满全国,其所用坯布完全由当地农村供给,这无形中提高了原白布的声誉,甚至在外地有些染厂其产品质量不高,也认为是坯布不良的原因。因而凡属潍县织的布,就成了各省市的抢手货,布商不远千里来收购、定购。织布户从无滞销积压之患,远销21个省70多个大城市,从中可窥见当时盛况。
潍县织布本是历代相传,铁机虽属更新换代,但仍是家庭手工业范畴,后人易于继承;当地有多家新兴机器铁工厂,盛产织布机,随时可买可修;这里靠近线纱基地青岛,原料充足;产品声誉在外,销路畅通,无倒闭之患,无滞销之忧;这么多的有利条件,自然会日趋繁荣。农民购机织布热潮,越来越高,至1936年进入鼎盛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1938年1月9日,日寇铁蹄踏进了潍城,农村遂即全部沦陷,所有织布户不得不销声匿迹。在日寇、汉奸的蹂躏下,织布机被大量破坏,加上地方杂牌军蜂起,各据一方,扩充势力,他们自办工厂制造枪炮弹雷,但农村中并无钢铁,大机上的铁制机件就成了搜刮抢夺的对象。十几年的劫难,偷偷保存下来的已经寥寥无几了。
1945年八路军解放了潍县部分农村,人民政府号召解放区人民生产自救,幸存下来的织布机才又开始转动。1948年4月潍县全境解放,广大织布业者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纷操旧业。他们将被毁坏的大机残骸,以拼凑、修理、代用等方法使之再生。不几年,隆隆织布声又到处可闻了,走在最前面的依然是潍河两岸。
解放后的潍县划为潍坊市,在党的领导下这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大进军中,纺织业、印染业又曾是首先腾飞。棉纺、棉织、化纤、印染、毛纺织、针织等门类,一一跨入先进行列。被列为全国重要纺织生产基地。
(潍坊市寒亭区政协供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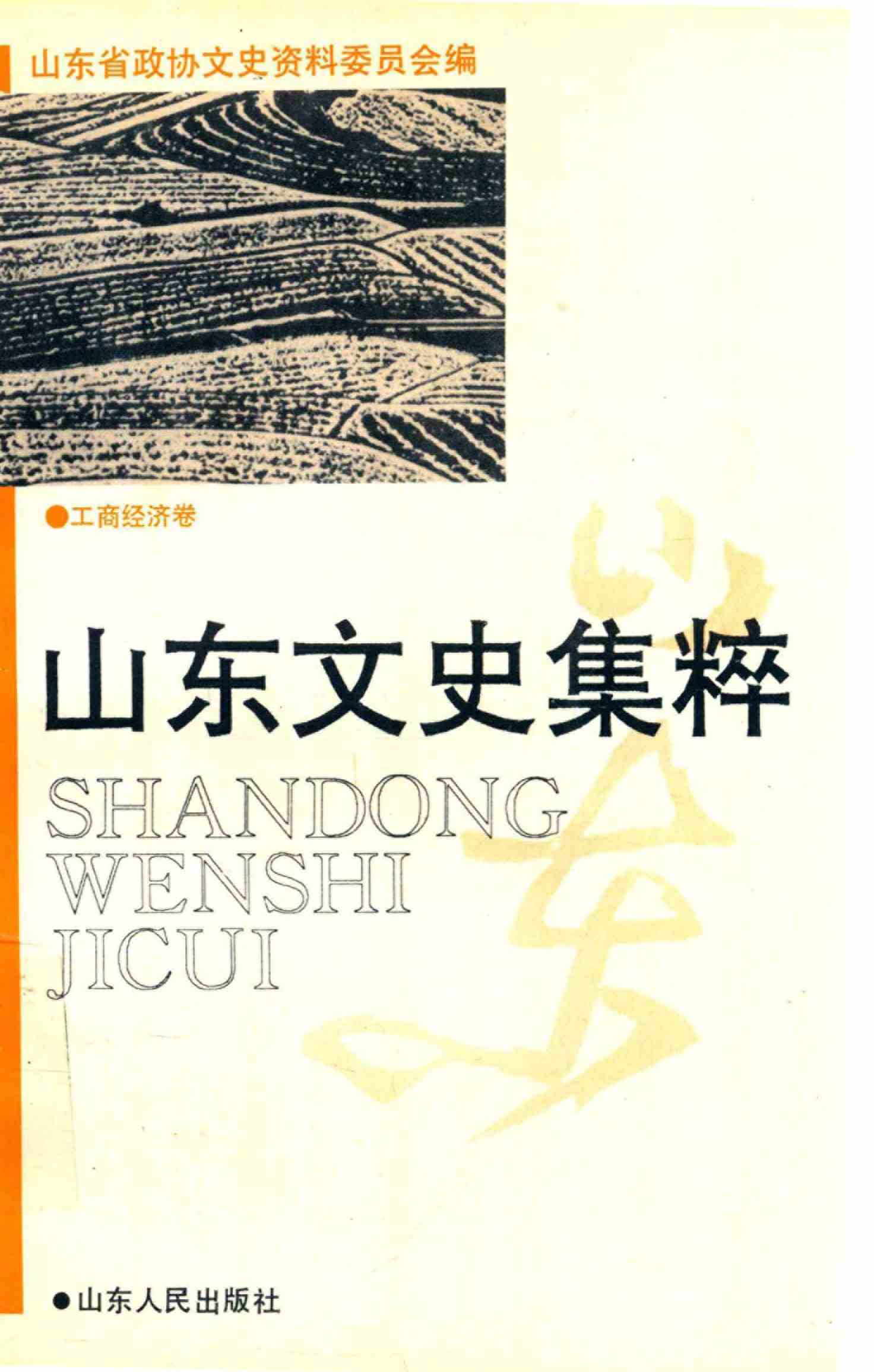
《山东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卷》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分为政治、军事、革命斗争、工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风物10卷,全书以真实丰富的史料,朴实流畅的文风,重点反映了自戊戌变法至建国前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山东省的重要史实。
阅读
相关地名
山东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