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宗族
| 内容出处: | 《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219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宗族 |
| 分类号: | C913.11 |
| 页数: | 28 |
| 页码: | 154-181 |
| 摘要: | 本章介绍了八井村雷姓畲族宗族分福、禄两房,形成了跨越几个自然村的宗族组织,以辈分和年龄的原则选举房长。 |
| 关键词: | 八井村 雷姓畲族 福禄两房 |
内容
分布在八井、横埭畲村的雷姓畲族,属罗源县松山镇牛洋支派,①传说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如东县,后迁入福建兴化的莆田一带。后迁至罗源,先住居罗源城西南的笔架山,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入迁现松山镇牛洋村,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分衍八井村。②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为迁界的关系,分别迁往吕洞、溪(今南洋)和尖山等地。康熙二十年(1681年)复界时回迁牛洋、八井,其后裔再分衍牛坪(已废)、横埭、杨家里、经布岩等处。八井村雷姓畲族宗族分福、禄两房,福房分居八井、横埭,禄房主要住八井,至今已繁衍17代,形成为一个跨越几个自然村的宗族组织。
第一节 宗族组织
八井村畲民以开基祖为近宗,构建了一个“宗族—房支—家族—家庭”的宗族体系。在这个血亲共同体中,由于没有福、禄两房共同的宗祠,同时由于没有族谱,人们的记忆又是有限的,所以福、禄两房在哪一代有共同的祖先,现在还不清楚。所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整个宗族更多地表现为是福、禄两个房分的组合。与此“虚拟”的宗族相比较,“房支”更是一个实在的实体,它以祠堂为中心,将数十上百户家庭维系在一起。八井村畲族分为福、禄两房,福房为长,禄房其次,其房支的开基祖现还不清楚。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八井行政村第一、第三村民小组的雷姓基本上都属福房,第二村民小组的雷姓则属于禄房;横埭村(属竹里行政村)的雷姓属于福房者为多,属于禄房者极少。八井新村与横埭村之间只隔着一条小溪,且同属福、禄两房,但彼此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由此可见居住地域对宗族内部关系有甚大影响。1990年以前,横埭、八井同属八井大队(1984年9月改为村),1990年行政区划变更后,横埭从八井村划出,与上竹里、下竹里同属竹里行政村,八井自然村与牛洋自然村同属八井行政村,并一直延续至今。
福房在人口数量上明显多于禄房,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往山脚平地搬迁之前,福房集中居住在两个区域,禄房则聚居在一个区域。虽区域不同,但彼此相隔实际不过咫尺。三个不同的住居区,以后便成为行政上划分村民小组(过去则为生产队)的主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们考虑到山脚平地交通的便利,遂陆续从半山腰的老村往下迁居,形成了今日福、禄两房杂居的居住格局。在八井畲村内,无论福、禄两房是分别聚居还是杂居,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始终都比较密切,长幼尊卑秩序井然。在我们所征集与抄录到的八井村畲族从清雍正年间到民国期间多达近300件的契约文书中,凡涉及族内典当借贷的,他们均以(堂)叔伯兄弟侄相称,族内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以前,福、禄两房各有一位房长,由房中辈数最高、年岁最长的人充任。房长是村落的自然领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每一房内,都专门留有几分田地,给房长耕种,收入归房长个人,也许是作为他为族众辛劳一年的一点补偿。房长辞世后,田地自动转让给新任房长。凡事关房内的一些公益性事情,如族谱的编撰和重修、祠堂的鼎建和修葺、祭祖的安排和实施、庙宇的修建和维护等,主要都由房长负责发起和主持。如遇有突发性事件,经众族人公议后,亦须得到房长的首肯。房内若出现严重纠纷,房长有义务进行仲裁。如果房与房之间发生纠纷,最终亦由两位房长出面调停。如果是和外村发生纠纷或冲突,则通常由房长等出面,会同当时最基层的政府人员如地保、铺长、乡长、保长等解决。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八井地区实行保甲制,八井畲村与牛洋村同属竹里保。保长由上面指派,最早是雷志东,两年后由雷坤珠接任。1940年,竹里保与小获保合并,保长为陈福福。①
1949年以后,宗族组织的政治、管理活动受到官方限制,房长在村落的领导角色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房长的产生所依据的只是辈分和年龄的原则,所以直到现在,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族人,仍然被雷姓族亲公认为所在房的房长,尽管事实上他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小。在福房,现在公认的房长是雷坤雨,他于1924年7月出生,2003年79岁;禄房房长是雷佺尧,他于1927年2月出生,今年76岁。二人虽同为房长,但遭遇迥异。雷坤雨无子嗣,由从起步镇护国村抱养的女儿雷伙妹招亲来延续香火,赘婿从连江县官坂招入,并改为雷姓,成为八井雷氏宗族的成员。他们为雷坤雨生了3个孙子,使雷坤雨延续香火的愿望和目的得以实现。在养女10多岁还未招亲时,雷坤雨急于解决香火继承的问题,不等养女招亲就先从竹里村抱养了1个孙子。然而,也许是因为过分溺爱和放纵,这位抱养来的孙子长大后却不争气,成天游手好闲、小偷小摸,被判3年劳教后,妻子虽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但也无法忍受他的行为而离婚改嫁到白塔乡去了。雷坤雨跟着养女一家生活,构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主干家庭,抱养来的孙子也分家另过。雷坤雨养女家纯以种植业为生计,因此家庭生活相对比较拮据。所以他经常衣衫褴褛,拄着根拐棍在村中闲荡。如果不是村民指认,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眼前这个瘦小的孤老头居然就是福房的房长。
雷佺尧的家庭情况与雷坤雨有点类似,但境况却是两样的。雷佺尧夫妇也没有亲生子女,他从罗源城关抱养了养女雷香桃(原姓吴),并通过养女招亲,招赘本村福房的雷信慈为“儿子”,雷信慈夫妇为雷佺尧夫妇生了2个孙子3个孙女。两个孙子与大孙女都已成家,大孙子雷可华有1男1女;二孙子有1女孩;大孙女有1男孩。所以从家庭香火繁衍的角度说,雷佺尧是儿孙绕膝,四世同堂,而且当了内外曾祖父。雷佺尧与雷坤雨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八井畲村中的“知识分子”。他年轻时跟随八井对面山上树楼村的法师蓝法吉(蓝得兴)学习闾山、茅山道法,在师父去世时,通过“奏名”仪式获得“法名”雷法莲,是八井畲村中有知识者。正因为这一机缘,雷佺尧比较注重其子孙的文化教育,亲自教孙子认字,并把他的法师知识传给了下代人。在他的关注下,他的养女雷香桃生于1955年,60年代受过小学教育,是当时村中读过小学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其大孙子雷可华生于1972年,高中毕业,2003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大孙女雷华妹(钗玉)1975年生,小学毕业。二孙子雷可良1977年生,初中毕业,并且是雷佺尧法师知识的继承人。二孙女雷伙玉生于1980年,中专毕业。三孙女雷金玉,1984年出生,现正在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就读。整个家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村里处于顶端,而且其儿子、孙子的家庭经济收入也都在村里属于中上等。自然,他也生活富足和无忧。在我们调查期间,身子骨硬朗的他,经常穿戴整洁,端坐在自家的新房前或村委会前的大榕树树阴下闭目养神,似乎在回忆昔日的往事。
无论过去或现在,房长的人选都必须是嫡生的,其他如抱养、过继或招亲的,即使辈分最高、年龄最长,也没有担任房长的资格。这类人家的子孙,要在抱养、过继、招亲后持续繁衍德的第三代,才有资格当房长。
福、禄两房都遵循共同的字行(字辈)原则,即同一辈分的人使用相同的一个字来起名,不同辈分则使用的字也不同。从第一代到第十七代,其字行顺序分别是: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朝—廷—乾—坤—志—信—可—知—贤。然而,在福房内,似乎自第十代即廷字辈开始,又确定了另一字行顺序:枝—大—向—章—传—世—德—恒—开。这是族人自述的一般性的字行顺序,但从其实际的运用来看,又经常出现变异现象。例如,雷辅铨的儿子本来是“朝”字辈,但除“朝泰”外,又有“枝相”、“枝迎”等名字,他们似乎与其他如“枝汤”等人共同构成了“枝”字辈。辅铨的孙子是“大”字辈,分别有大祚、大云、大马、大祯、大玉、大雨等人,按照字行原则,其曾孙应该是“向”字辈,但实际上又转回“乾”字辈,分别是“乾锐”、“乾金”、“乾标”、“乾炳”等。①再往后,则按“坤—志—信—可—知”的字行顺序起名。
在汉族社会中,字行的分衍,往往便意味着房支的裂变。但在八井村,似乎自明代至今,一直就存在福、禄两房,并未裂变产生出新的建有祠堂的房支。这大概就是他们不严格遵循字行规则的原因所在。即使在现代,情况也大致如此。如雷德明(1951年5月出生)属“德”字辈,他的儿孙的排行应该是“恒”和“开”,但实际上他的儿子取名叫雷知文(1976年7月出生),孙子取名叫雷贤镇(1999年10月出生)。在八井畲村,使用“恒”、“开”字行命名的人极为罕见。到目前为止,“贤”字辈年龄最大的已有24岁(雷贤坤,1978年3月出生,未婚),已达到婚育的年龄,所以他们急欲制定出新的字行,以便将这一区别世系的命名原则延续下去。
八井村畲族和汉族一样,遵循“父之党为宗族”的原则,族中女性的名字并不按字行命名,只在族谱上注明“女,××,配某地某人”。现在,除极少数年轻人外,绝大多数族人都仍然按照字行给子孙命名。依据各自的名字,族人能够轻而易举就辨别出彼此的辈分来。如此,不仅宗族内部的长幼秩序井然,而且宗族的世系序列也非常明确。
八井村畲民的名字均为复名,即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依字行确定,俗称“字头”,第二个字则自由选择,如“可”字辈起名“可良”、“可寿”、“可华”、“可木”等。在民国时期,族中男性除依字行确定的族名(谱名)外,还有字、号,并在族谱上予以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字、号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有号的人就更为罕见了。大多数族人还另有乳名,即孩提时代父母对他们的爱称,如“阿弟”、“阿根”、“细仔”等等。长大成人后,仍继续在族亲之间使用。但在正式场合,如入学注册、户籍登记等,这个名字则不再使用。
少数人还有法名。法名又叫“奏名”或“醮名”。在很多畲族族谱中,都可以看到法名的记录。据称,法名是畲民男女年届16岁经历一种类似于成年礼的仪式后所起的名字。这种仪式被称为“传师学师”或“作序头”、“传法录入”等。经过这种仪式的男女,被冠以“法名”,男性“法名”前都冠以“法”字,女性则后缀以“婆神”二字。①但是在八井畲村,只有具有法师(道士)的身份且师傅已过世的族人,才能取得法名。如禄房房长雷佺尧,其法名叫雷法莲。他曾经师从树楼村的蓝得兴(法名为蓝法吉)习法,师傅过世后取得法名。其孙子雷可良(1977年12月出生)跟随他学做道士,但因为他还健在,所以雷可良至今未取得法名,而只能用其祖父的法名做科仪。在八井畲村,也未曾发现女性有法名的。
家庭是宗族的最小单位,通过家庭的阄分、裂变,房支得以扩容,宗族力量也进一步增强。在八井村,一般结婚半年以后,新婚夫妇未及生育,就先行分家了,所以累世同居的现象极为少见。谚语也说:“娶一门媳妇,分一次家。”按照过去的习俗,分家通常由母舅主持,房内族亲参与评判。分配的财产为生产生活资料,如田园山场、房屋住所等。旧的炉灶归长子,其他儿子另起炉灶,这是取“传香火”之意。即使父母健在,一般也不留“养老田”,而是和未婚的儿子共同生活。如果儿子都已成家,父母的生活则由几个儿子共同供养。田产的分配,对长子有适当的倾斜,俗称“长子田”,但比例一般都较小。房屋的分配,如果仅有两子,根据“左昭右穆”的原则,则长子分左边厢房,次子分右边厢房,前厅与后厅则公用。现在的分家已比较简单,除非特殊情况,一般父母主持即可,并不专门恭请母舅出面,连族亲也不经常参与。对长子也没有明显的照顾,通常不分长幼,平均进行分配。待弟弟将来结婚成家时,为兄者再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考虑资助的额度。
在八井畲村,家庭之上,福、禄两个大房之下,实际上还存在着家族与小房支。例如上述所提及的雷佺尧和他的儿孙们的关系即为一例。雷佺尧家现已分家,他自己单过,形成一单身家庭;其养女及其丈夫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大孙子和其妻子和两个未婚的子女生活,这又形成为两个核心家庭;雷佺尧的老婆则与二孙子一家一起生活,形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主干家庭,而所有这些家庭都属于雷佺尧的派下。换言之,在雷佺尧的派下有四个家庭,即一个单身家庭,两个核心家庭和一个不完整的主干家庭。这些家庭的关系,即雷佺尧家族底下的几个家庭的关系。换句话说,大家庭分裂后形成的几个家庭,通常会在一个最近的共祖名下构成为一个家庭的联合体——家族。至于这种家族可以追溯到第几代,则要看其人口的多寡而定。人口少了,可能追溯得远些,人口多,则可能追溯得近些。而对于这种家族中的关系,八井畲民用“一家亲”来表述。
在家族之上,还存在着一些家族之上的小房支。这种小房支虽然没有明显的宗族象征物如专事于崇拜某位祖先的场所,但它确实存在,并经常在日常的仪式事务如婚礼、丧礼中体现出来。由于这种小房支没有明确的宗族象征物来体现,而且多以向上追溯到某代祖先来计算,所以我们以某某房支来叙说,可能要容易与清楚些。例如乾珍是八井雷姓的十一世祖之一,其派下现已繁衍到第十六代,现大约有十几个家庭(参见图6-1)。在这一层次上,他们属于人数较多的房支,彼此之间都比较亲近。其实这类房支的亲堂关系,是向上追溯的,如信银与信金为同胞兄弟,信银与信钦、信财为隔腹兄弟(公兄弟),他们同是乾谋房支的成员。信银、信钦与信开、信钗等虽是同辈的人,但他们要追溯到雷氏的六世祖时,才为同一房支的人。因为信银、信钦等为其六世祖的二儿子的派下,而信开、信钗等为其六世祖三儿子的派下,所以追到他们的六世祖,他们都属于同一房派。其他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此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八井畲村的畲民主要实行民族内部通婚,与周边如竹里、树楼等村,或起步、碧里、白塔乡等的雷、蓝姓畲族乡村互为婚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以后,由于三代以外的旁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受法律所保护,八井村原“祠堂内不能婚配”的传统习俗被打破,宗族内婚姻骤然增加,甚至房内婚姻也出现不少,但原则是五服以内不可婚。以雷可孝(1944年12月出生)为例,他有7个兄弟姐妹,除大哥雷可忠未婚先逝外,其余6个兄弟姐妹中有2个属宗族内婚配,占婚配总数的33%(参见图6-1)。在其第2代婚姻中,属于宗族内婚配的有9对,占婚配总数20对的45%。第3代已婚的只有2例,便有1例属宗族内婚配,所占比例暂时也是50%。雷可孝家的例子也许是一个特例,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八井畲村1949年以后宗族内部通婚渐趋增加的真实情况。
雷可孝的妻子雷翠云(1942年2月出生)原本姓蓝,父亲是邻近的起步镇人,母亲则是由八井畲村嫁出去的。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于是携4个子女回到八井村投靠娘家。以后再从竹里村蓝姓招了一门亲,并生了翠云最小的3个弟弟。她(他)们7个兄弟姐妹本来都姓蓝,但据说因为一时的疏忽,凡住居八井畲村的,其户籍上甚至身份证上的姓氏都变成了雷姓,包括他们的嫡系后代。对于这一“疏忽”,他们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表示希望给他们正名,恢复他们的“蓝”姓。无论如何,在翠云兄弟姐妹及其第2代的婚姻中,除翠云本人外,倒是没有一例属于村内通婚的(参见图6-2)。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
宗族内部大量通婚的结果,导致宗族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上,宗族是某一男性祖先的后代累世聚居所形成的一个血亲团体。在宗族组织中,核心成员是男性,它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进行大规模间接的宗族间的交换。根据交换的原则,族中的女性成员都不留在宗族内部,因此宗族的血缘主要通过男性的世系延续下去。但是在八井村畲族中,由于宗族内部通婚增多,导致很多女性成员留在宗族内部,并未进入交换的领域,从而使得宗族的血缘不仅通过男性成员,而且通过女性成员向下延续。由是,宗族遂演变成一个集血缘和姻缘于一体,既包括血亲又包括姻亲的社会组织。宗族内部的成员之间,也由单纯依靠血缘相联系,转变成为可能既有血缘上的联系,又有姻缘上的联系。宗亲之间的亲属关系,亦随之不仅是血亲关系,而且可能有姻亲关系。
宗族关系的这种变化,势必导致宗族内部在亲属态度和亲属行为上的相应变化。具体地说,这种变化可能是正负面兼具:一方面,它可能造成亲属称谓上的混乱,进而影响到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宗族内部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宗族成员从过去的生产生活中主要依靠数代范围内的血亲,扩展到可以依靠一定数量的姻亲。就前者而言,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也许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宗族可能会发展出一套相应的机制,来对这种后果进行匡正,可惜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未能就此展开更进一步的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另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通婚,使亲属圈的范围得以扩大,个人或家庭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增加。以雷可孝家为例,仅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的第二代就在八井村组建家庭13个(以结婚为标准),其妻雷(蓝)翠云的兄弟姐妹的第二代又在八井村组建家庭2个,加上第三代的2个,一共是17个。在这17个家庭中,计有10个家庭建立在宗族内通婚的基础之上。这样,即使假定所联姻的10个对象全都没有兄弟姐妹,他们至少也在村落中建立起总共达27户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占八井村总户数113户的1/4弱,①即约24%。如果考虑到宗族内的通婚对象多数必定有兄弟姐妹,这个比例实际上还要大,估计至少可以达到30%以上,即1:3强。如此庞大的一个血亲加姻亲关系网络在宗族体系中存在,不可避免地对宗族组织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村民就反映说,雷可孝家的亲属关系网络在近年来的村委会选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八井村宗族组织中,除了以血亲和姻亲为核心构筑的亲属关系网络外,还有一种被称为“人情谊会”的临时性互助组织,作为对亲属关系的补充。组织“人情谊会”的目的主要在于集中族众的经济力量,解决族人在结婚、建房、做小买卖等事情上所面临的资金周转问题。结会所涉及的金额一般不大,每一期少者200元,多者500元,通常为300元。利息为年息,通常是15%,理论上由全体会员共同享受。由于参加一个会所能获得的资金总额有限,所以有的人可能同时参加几个不同的会。“人情谊会”的会首(俗称“会头”)通常由召集和发起人充任,通常情况下,他也是最急需使用资金的人。参加“人情谊会”的成员一般为族中关系较好又有一定信誉的族亲,如果招募到足够的会员确实有困难,会首会考虑敦请外族中的亲戚或朋友参与。
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常见的“标会”不同,“人情谊会”在资金的使用上并不采取“投标”的方式,而是按照事先的约定依顺序使用。在结会之初,会首会出面协调,根据会员各自可预见的需要使用较大额资金的时间,确定好使用资金的先后顺序。“人情谊会”通常由10~12人组成,可以是月会,也可以是季会,分别按月份或季度上缴会资,每缴纳一次为一期。因为大多数村民的经济来源有限,所以月会事实上比较少见,更多见的是季会。但即便是季会,其实也并不经常按季度缴纳会资,而是一年中分为三次(即三期),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下半年为农作物收成的季节,会员上缴会资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另一方面,结婚、建房等大事也大多安排在下半年操办。
假如一个季会有12人参加,每期会资300元,其具体的运作办法是:第一年首期,会员每人向会首缴纳300元,共计3300元。第二期,每位会员应向会员甲缴纳300元,但因为会首已经使用过会资,所以他要另外缴纳15%共计45元的利息。这45元利息其他10人平分,每人4.5元,这样其他10人实际上只要缴纳295.5元就可以了。会员甲实际收取总会资3300元。第三期,会首和会员甲需向会员乙缴纳345元,其中属利息的90元由其余9人分享,每位会员10元,所以他们每人实际上只要缴纳290元即可。会员乙实际收到会资也是3300元。第二年的首期,会首、会员甲和会员乙分别向会员丙缴纳345元,利息部分共计135元属于其他8位会员,每人可分得约17元。这样,其他8位会员分别只要向会员丙缴纳283元即可。以后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一期,待到所有12位会员都收缴到会资后,此一轮的“人情谊会”方告结束。
虽然“人情谊会”中涉及高达15%的年利息,但因为这些利息基本上由会员共同分享,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属于宗族内部公益性的互助组织。况且,作为召集人和发起者的会首,他本人并未从中获取任何额外的利益。相反,因为他第一个使用会资,所以他为此付出的利息其实也比所有其他会员都要多。从实惠的角度来看,最后一个获取会资的会员无疑是得利最多者,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他所承担的意外风险也最大。这种互助性的民间组织,一方面有效地弥补了山区农村在资金来源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宗族内部族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其他汉族地区的影响,在八井村也出现了少数的“标会”组织,但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
第二节 宗族象征
祠堂、族谱是宗族的重要象征。在八井村畲族中,除祠堂、族谱外,还有祖杖、祖图、祖牌等宗族象征物。从表面来看,八井村畲民很重视祖先崇拜,其崇拜的对象包括远祖与近宗两部分,远祖是指“忠勇王盘瓠”(也称“龙麒”)、“立国侯雷巨祐”等盘瓠传说中的始祖,近宗则是八井村的始迁祖雷安居、雷安和兄弟及其以下的历代祖先。但是实际上,与汉族的祖先崇拜相信祖先会保佑他们子孙的简单态度不同,八井村畲民对祖先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远祖属于“神灵”的系统,近宗则属于“鬼灵”的系统。对于隐含在神话传说中的远祖,他们深知这些神灵与族人的关系十分遥远,并不会对他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任何实际影响,所以对它们表现为一种对“神”的崇拜,祭祀的目的也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族群上的认同。而对于以开基祖为代表的一系列近宗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视之为无法亲近的“鬼”,祭祀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或者只是为了讨好近宗的鬼灵,使它们不加害于自己的后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对于近宗的鬼灵表现出一种时时处处加以提防的心理。
这种提防心理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对待族谱、祖图、祖杖等宗族象征物以及与祖先相关的一切实物的态度上。他们相信,这些物品,只要是与祖先相关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神性,就会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可能的不利影响。显然,这是一种泛灵信仰,它使得八井村畲民对此类物品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只要不是自己非常熟悉的近亲,凡是他们用过或与他们有关的物品,都尽量不要去接触它,否则就可能给自己带来祸害。很明显地,在八井村畲民对于近宗的态度和他们的祖先崇拜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跨越的矛盾,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崇拜祖先,就势必相信祖先灵魂的庇佑,而不是对他们采取提防的态度。所以,我们宁可相信,祖先崇拜并非畲族信仰的原生形态,而是因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其祖先崇拜中隐含的这种矛盾。
根据这种泛灵信仰,与祖先密切关联的物品是不宜放在住宅内的,而只能集中放在祠堂中,或其他远离住宅的地方。例如,我们从村民雷可春处征集并抄录了一批从清代到民国期间的契约文书,新任村主任和他的太太就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们带到家中①,放在村委会办公室就可以了,否则他们“会害怕”(村主任太太的原话)。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和紧张心理,我们调查组要离开八井村时,才直接将这些契约文书和抄件从村委会带上了公共汽车。他们认为,如果将此类物品放置在住宅中,可能会给家人带来厄运。
祠堂:祠堂是宗族的最重要象征,通过在祠堂内定期举行的各种集体祭祀仪式,八井村畲民既实现了与远祖和近宗的心灵沟通,又达成了内部的团结和整合。祠堂既是神圣的场所,是祖先神灵的寄托所在,又是世俗的场所,是宗族聚会、训诫子弟和宣导宗法族规的所在。福房、禄房原各有自己的祠堂。福房祠堂位于祠堂厝,1934年曾经作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现几近于坍塌。禄房祠堂位于当中厝,于1946年被龙卷风刮倒,之后一直到几年前未能重建。近年来禄房在原地盖了间6平方米的三面墙小屋,内放有一些个人家中使用的“祖宗套”,但似乎也没听说有举行集体的公共祭祀仪式。由于没有了祠堂这种崇敬、祭祀祖先的场所,他们已多年未举行祭祖活动,就连祖杖、祖牌、祖图和族谱等宗族象征物,也已不见了踪影。重新修复祠堂,成为族人的一大心愿,尤其对人口占多数的福房族人而言。由于一些族人经济条件非常有限,虽经多年努力,至今未能如愿。部分村落精英至今仍在为此事四处奔波,在他们看来,重新整修祠堂和编撰族谱是当前增强宗族凝聚力的当务之急,也是衡量新一代精英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座祠堂于何时营建已不可考,但估计不晚于清代中叶。其依据有二:其一,八井村毗邻汉族村落罗厝里,即便以旧村论,两者相距也不过只有二三里地。从清代保留至今的契约文书来看,八井村与罗厝里甚至县城汉族之间的经济往来频繁,以至到解放初期,两村之间的山场田地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在经济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八井村畲族文化势必受到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仿照汉族宗族修建祠堂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二,在清代中期,八井村经济发达,甚至出现了像雷君恒这样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虽然族人都言之凿凿地解释,雷君恒幼年丧父母,由哥嫂抚养成人,18岁之前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只是在捡到1瓮金子之后才发迹,但他大量向周边汉族典买田地却是不争的史实。坐落于祠堂厝角落的两座规模宏大的“八扇房”,都是雷君恒自己出资兴建的,一座属其派下的长房,一座属二房、三房,在20世纪90年代迁出之前,居住着9户和13户人家,其中还有几间房专门作为房中子弟修习功课的书院。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兴修祠堂的可能性应该最大。
当然,按照一般的惯例,宗族的祠堂不太可能由某一人修建,但诸如雷君恒等族中财力雄厚的富户,一定是祠堂兴建的主要倡议人和资金的捐助者。其他一般的族人,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总之,祠堂的兴建既是宗族经济实力的体现,又是宗族成员团结协作的结果。在形制上,八井村畲族祠堂与周边的汉族祠堂基本类同,但是它里面所存放的宗族象征物无疑要比周边的汉族祠堂多,包括族谱、祖杖、祖图、祖牌、香炉、楹联等。这6件象征物,通常被称为畲族的“镇祠之宝”。八井村畲族对祠堂的内外环境极其重视,不仅祠堂内的神龛、几案要保持洁净,就连祠堂前后的地块都要勤加打扫。祠堂有“值祭”,由族中各户依次承担,除负责每月初一、十五日的焚香点烛外,就是保证祠堂的内外整洁。根据族规,如果发现祠堂不洁净,“值祭”必须受罚,处罚方式是继续轮值。
祠堂内供奉着自始迁祖以下的历代先祖的“神主”牌位,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一日为房族的祭祖日期。一般人死后便立一牌位,每年的忌日在家中祭祀,待三四代之后即放入祠堂,进入祖先的灵魂系统。进神主牌位入祠,每人缴纳240文。因为现在祠堂已废,所以祖先牌位都是和本境的各类神灵的神位或神像一道,放置在住宅中厅堂正中的神龛上。牌位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不具体书写姓名的远祖近宗牌位,上书“冯翊郡雷
家堂上历代远近宗亲香位”等,这种牌位,当地畲民称之为“祖宗套”;另一类是去世不久者的个人牌位,上书“显考雷公××之神主香位”或“显考××雷府孺人之神主香位”。有的则是将夫妇合写在一起的牌位,上一般书写“显考雷公××妣×氏孺人之神主香位”。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家人需焚香点烛。
族谱:族谱是宗族谱系的物化形式,其撰修时间应该与祠堂的鼎建大体同步。在八井村畲民看来,编修族谱、兴建祠堂和祭拜祖宗是宗族中重要的三件大事。其中,编修族谱又是重中之重,因为族谱用文字的形式,追溯了宗族的远古来源,历数了开基祖为宗族的生存与繁衍所付出的艰辛。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谱系的文字记载,每一个族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超越时空的障碍,把个人与其他族亲、与历代先祖联结在一起。对于个人而言,由此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对于宗族而言,由此产生一种血缘上的认同。这种血缘的认同再通过地缘的聚居,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内聚力,从而构成为宗族组织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当然,即使在没有族谱的情况下,族人也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宗族谱系往后延续,但这种方式毕竟没有谱牒记载那样持久、那样明确。
根据鼎建祠堂的时间来推测,八井村族谱编修的时间应该也是在清代中期。编修族谱的事宜由房长主持,配以若干族人主办。各家提供本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子嗣婚嫁状况和墓葬建造时间、方位等,这些内容称为“家状”。修谱先生根据各家提供的“家状”,构拟出宗族繁衍的世系图。当地人也认为,修谱者如果没有把族中的所有人的关系记录清楚,以后那些没上谱者的阴魂会找他的麻烦,使他不得安宁。谱内世讳的确立按“排字世项”的原则进行,载于族谱中的正式名字称为“谱名”,由“讳名(世名)、字、行第”三者组成,它表明族人在族中的世属和排行。人死以后,牌位和墓碑上用的都是谱名。如前所述,现今的八井村民并不遵循行第的原则,而是依世代所属字行,第一个字按字行规则取用,如“可”、“知”、“贤”等,第二个字则由父母随意确定,只要尽量不与其他族人重复便可。
八井村禄房的祠堂倒塌得早,族谱在多年前就不见了。福房的族谱原来一直就放置在破漏的祠堂内,大约七八年前,被一个小偷连同祠堂内的其他一些物品一起偷走,也不知去向了。
以前,每年农历的七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族谱被从祠堂内的神龛上拿下来,放在厅堂正中的几案上,供众族亲展阅。据看过族谱的族人回忆,像其他畲族族谱一样,福房族谱中有“谱序”、“凡例”、“敕书姓氏封”、“得赐三姓源流纪”、“龙首师杖志”、“历朝封赠”、“差扰”、“高辛驸马龙公墓图”、“立国侯祐像赞”、“字行”等内容,这些被称为“谱头”。在“谱头”之后,是福房雷姓的世系图,包括分居在横埭等地的宗亲。
祖杖:祖杖又称“龙首师杖”或“法杖”,是八井村畲族显示远祖权威的象征物。平时和祖图、族谱一起存放于祠堂正厅上方左右两侧的木柜中,不轻易示人。举行祭祀仪式时,向族众展示,展示完毕即放回原处。祖杖长约四尺,头部雕刻成龙头状,今已不存。距离八井村仅数里的树楼村蓝姓族谱中有《龙首师杖志》,其记曰:“按盘瓠王生于帝喾高辛氏四十五年五月初五日,时至帝尧陶唐氏廿一年六月廿七日,盘瓠王游山伏猎,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登树岔而卒。十七日得尸而归,同朝奉上。帝思功臣生既非怀于人胎,死复不归乎中土,命将士将树砍回,召青州范氏刻盘瓠王颜像,名曰‘师杖’,谥为忠勇王,每朔望致祭。四月初八日丑时葬于凤凰山,坐卯向酉,立有石人石马石麒麟。为记。”①
祖图:祖图又称“太公图”或“长联”,是关于盘瓠传说的实物资料,于每年的正月初五日“开年驾”(表示新年结束,要开始生产活动了)时,横挂在祠堂正厅的墙壁上,向族众展示一天,意在向族人宣导远祖的业绩。翌日清晨,便小心地珍藏起来。据族中老者介绍,八井村畲族祖图为一条状横幅长卷,长1米左右,底为麻布,上面浓墨重彩,图文并茂,描绘了盘瓠变身、征番有功、招驸马、受封、狩猎等有关盘瓠传说的历史场景。虽族人爱护有加,惜因祠堂毁损,早已不知去向。
祖牌:祖牌又称“龙牌”,系祖先的牌位,一般一位祖先就有一个祖牌。祖牌为木制品,上雕以纹饰,并用文字注明系哪位祖先的牌位。祖牌放置于祠堂正座的祖龛内,其雕制和进龛都要选择吉日吉时,不得马虎。凡属众家的牌位由祠堂出资修造,属各家的牌位由各家自行修造,由此导致祖龛内的祖牌虽造型类似,但装饰不一。有的祖牌甚至镶有金箔,做工也十分精致、考究。现在,因祠堂无法放置,祖牌已被家中的牌位所取代。在村民雷可孝家中,我们发现其为未婚先逝的大哥设立的一块牌位,上书“永言孝思显考雷可忠历代远近宗亲香位曾孙雷贤斌祀”。经询问得知,雷可斌尚未成年,系雷可孝的孙子,名义上过继给伯祖雷可忠。但既是过继,又为何在辈分上降了一辈,由“孙”变成“曾孙”?我们不得而知。
香炉:香炉为铜制,代表着香火,所以受到八井村畲民的格外重视。它既是祠堂内举行祭祀仪式时的必需物,也是八井畲村宗族的象征物之一。
楹联:楹联由族中或族外的儒士撰写,在各地祠堂内均可见。它以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宗族的历史和人文。和周边的汉族相比较,八井村畲族的楹联其特殊性在于,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惟内容始终保持不变。遗憾的是,在八井畲村福房祠堂内,我们连一对楹联也没有找到,相反,倒是有一些零星的“文革”时期的标语和已故领袖人物的画像。
第三节 宗族活动
宗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其团体性体现在与全体族众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中,反过来,通过这一系列与全体族众相关的活动,宗族组织的团体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活动可以是有组织的,如祭祖、宗教性集会,也可以是自发进行的,如生产中的合作、生活中的互助等。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主要以地域为依据,所以在乡村一级特别是村级行政组织中,行政区划与宗族组织出现了部分重叠。特别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生产活动的组织往往是以房份为单位,所以出现了行政村与宗族、村民小组与房支难以分割的状况。以八井畲村为例,八井行政村包括八井和牛洋两个自然村,它们同属一个宗族。在八井行政村内,第二村民小组与禄房对应,第一、三村民小组分别与福房的两个房支相对应。由于行政区划与宗族组织的重叠,现阶段很多宗族组织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活动的形式来举行。
每年农历七月十一日的祭祖仪式,曾经是八井村雷姓宗族中最为隆重的宗族活动。祭祖由族中各户轮流主办,从七月一日起,就开始拟定祭祖祝文,用为祭祖时诵读。祭祖时,需陈列祖图、祖杖、族谱等。主祭人为族中房长,陪祭人为每家家长,限20岁以上成丁,无男则女代。祭祖时有通赞2名、引赞2名、读祝文者2名、司众钱1名、司箔1名,均为族中有名望和地位者。八井村没有祭田,祭祖的费用由各户平均分担。捐立田租1000斤者,公立禄位,永垂后裔。捐钱100两修建祠堂者,也有禄位。结婚要纳喜钱100文,生男孩要纳喜钱60文,祭祖时交纳,作为祭祖经费。祭祖之前,要清扫祠堂、洗涤祭具、陈设器皿、备足祭品。祭品不作定例,可以随时斟酌,但不得用不洁或减价的物品,否则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祭祖之日,午夜子时鸣铳一响,族人即便起床,盥洗准备;丑时鸣铳两响,主祭和陪祭盛服入祠;寅时鸣铳三响,族人毕集,宣读祭文,集体致祭。礼毕,族众会餐,俗称“饮祭”。①在喧哗的聚餐中,宗亲之间的亲情得以提升。
时至今日,虽然全族性的祭祖仪式暂时消失了,但家族的墓祭仪式仍然保留下来。每年清明时节和白露节气,同一家族的族亲带上祭品,到祖先的坟墓前祭扫。墓祭由家族中的各户轮流主办,与祠堂祭祖相比,祭品比较简单,一般也不举行会餐。近些年来,墓祭的对象已逐渐简化为高祖及其以下的祖先。村民雷可寿解释说,因为历年墓祭都没有给族人带来明显的好运,所以渐渐地就放弃不祭了。例如,雷君恒及其裔孙雷辅铨的坟墓占地都不小,墓制也非常奢华,但现在墓碑上都布满了青苔,周边杂草丛生,甚至长出了小树,以至我们要带上镰刀、木棍,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来到墓前,勉强看清碑文。很明显,这两座墓都已多年未祭扫,况且雷君恒还曾经是清代中期族中的豪富。
除祠祭、墓祭外,还有家祭。祠祭仅在七月十一日及其他重大节日时举行,墓祭集中于清明节和白露,家祭则在平时和一般节日于家中进行。三者之中,祠祭最为隆重,家祭最为简单。家祭通常由家中妇女操办,陈设些许蔬果茶品,焚香点烛就可以了。虽然家祭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是私人性的,与宗族性的祠堂祭祖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也有别于家族性的墓祭。实际上,三者分别代表了宗族、家族和家户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空间。
由于宗族性祠祭活动的消失、家族性墓祭活动的淡化及其他一些可能的集体活动(如赛歌)的失却,八井村雷姓宗族组织的活动已浓缩在一些重大的节庆、婚丧喜事的操办和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中。就重大节庆而言,“做岁”、“上灯”及其他6个节日是宗族活动得以开展的主要机会和场合。
做岁:正月初一或十五日,以分组为单位,由上一年度轮耕“岁田”的家户,从“岁田”的收成中支出约200斤稻谷,到白马宫致祭,晚上分组成员在白马宫会餐,就餐者通常为家中的男性长者。“岁田”约有2亩,实行生产责任时专门划拨出来,多为山田,可耕种一季,亩产糯谷约300斤,杂交稻谷500多斤。每个村民小组又分成2~3个分组,每组7~8户至10余户不等,视总户数多少而定。每个分组的家户数实际上是不固定的,因为随着分组成员家庭的析分,每组的户数也在相应增加。但显然,这种户数的增长是缓慢的。据雷可寿称,他所在的分组属第一村民小组,共有16户,至今已轮值至第二轮末,他家是最后一个轮值户。轮值户的确定,系由抽签产生。在民国时期,则依商议而定。在第三村民小组内,由于户数相对较少,所以他们通常不再分组。前一年有喜事的村民,如盖房、娶媳妇、生育(无论男女)等,会在聚餐时专门给大家散烟。烟的质量和数量视各家经济情况而定,或2~3元一包,或7~8元一包,少的人均散发1~2支,多的每人一包。
从常理上来判断,“做岁”应该是在正月初一日,而不应该也包括正月十五日,因为“岁”字在八井村畲族的语言中也是“年”的意思。在一份年代大约为清代中后期的文档中,有“雷子英,九分正;辅登,应乙分五厘;辅和,应乙分五厘,拨元宵赛”的记录。我们据此初步判断,至少在清代期间,八井村畲族曾经有举办“元宵赛”的习俗。而且,可能还有专门用于举办“元宵赛”的“赛田”。在一份有关“赛田”的买卖合同中,甚至还注明有“大小鼓全堂,又碗壹付”,而这些物件通常是集体聚餐所需的。该合同如下:
立卖断赛田根约雷大会自己手置有赛田壹号,坐属拜井里小获地方,土名俗叫仔田壹号,载租谷肆百贰拾斤大称。今因无钱乏用,即将此佃田托中到引断根于堂兄大云处为业。三面言议,得出断价钱壹仟肆百文。其钱立断之日同中亲手收讫,其田即付钱主耕作纳租。其田价足心愿,葛藤以了,日后子孙不得言购言赎,亦不敢生端枝节之理。但此田是(大)会自己之口,与亲堂伯叔侄无干,日前并未曾重张典当他人财物。倘有不明,系是(大)会出头抵当,不涉钱主之事。两家情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卖断赛田根约壹纸为照。
又及:口大小鼓全堂,又碗壹付,再照。
中见代字钱陆拾四文,再照。
中见代字 堂侄 向宾
光绪五年贰月 日立卖断赛田根约 雷大会
该合同留给我们的疑问是:既是为“元宵赛”所置的“赛田”,又为何是属于个人的,且转让给了族人?故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断定所谓“赛田”就是专门为“元宵赛”而置,更无法探明“元宵赛”的具体运作情形。
上灯:正月十一至十八日,以分组为单位,由轮值户出面,向其他家户每户收取10到20元钱,作为祭祀和会餐的开支。以前,以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组织。考虑到户数众多,组织不易,现在才改由在村民小组的范围内分组进行。具体的时间安排是:第一村民小组,十一至十三日;第二村民小组,十四至十六日;第三村民小组,十七至十八日。日期有长短之别,主要原因是每个村民小组的户数不等。第三村民小组家户最少,共25户,第一村民小组的家户数最多,共43户,第二村民小组40户。在白马宫内,可同时容纳约12桌共120左右人就餐。重要的是,各分组中的家户构成,与“做岁”时进行分组的家户构成并不相同,虽然它们也有部分重叠。
无论是在“做岁”或是“上灯”的活动中,从表面来看,家户之间的这种组合都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但事实上,这种组合都遵循一定的地域原则,只不过这种地域原则被掩盖在村民小组的行政区划之下,因为在八井村和在其他行政村一样,村民小组的划分大体上是以居住区域为标准的。民国时期此两项活动开展的情况,更印证了这一构成原则。在民国时期,八井村有“四境”之分,分别对应着八井村四个大的居住区域。在举行“做岁”或“上灯”活动时,是以一“境”作为单位的。那时,每一境也都有自己公共的“岁田”,境内实行轮值耕种,收成的一部分(也是约200斤稻谷)作为活动的开支。作为轮值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部分来源,那时的“岁田”得到村民的重视。他们辛勤耕耘,力争有一个好的收成。而现在,“岁田”经常被抛荒,活动开支改由轮值户自己掏钱。
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日。各地畲族均重视“二月二”,但说法不一,有的地方认为是“会亲节”,有的地方认为是“神节”甚或“种竹日”。①八井村畲民认为,土地公能保佑生产不受灾害,给村民带来财运。在祭拜土地公及随后的会餐中,“做岁”或“上灯”活动中的分组原则均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自由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的对象通常为自己的朋友或亲戚,基本上是本族范围内的,也可以是外村的,唯人数以10~12人即一桌为限。所需经费由大家共同捐资,多少由各人自己决定,而不必是平均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一般会多出资一些。有理由相信,此次仪式性活动为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提供了一次展示财力的机会,而经济实力是获得和保持在村落中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每年的土地公诞辰日,这样的临时性组合都会出现好多个。
做岁、上灯、祭拜土地公等这一系列民俗活动,无疑可视为宗族活动之一种,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宗族活动的延伸和补充。因为在八井畲村,属于整个宗族的大宗祠未能建构起来,所以村庙建筑白马宫,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宗族活动的场所。白马宫属宗教建筑,修建在村落的古村口,门前的小路是以前进出村落的要道,供奉的神祇主要是当境神主白马王,其次是临水夫人、五显大帝和土地公。因为全村性的活动多在白马宫内举行,所以它们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与地方宗教信仰有割不断的联系。在周边的汉族村落如罗厝里、小获等,虽然也都有村庙白马宫,但仅限于神灵诞辰日的各家祭祀,而没有像八井村这样的集体性聚餐活动。
除做岁、上灯这两次在新年期间举行的活动外,在白马宫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共有6次。为了确保这6次活动都能举行,村落约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负责:第一村民小组,三月十三日白马王生日和八月十三日左、右将爷生日;第二村民小组,五月五日端午节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冬至;第三村民小组,二月二日土地公诞辰和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每个村民小组内,又各分成两个组,分别负责一次活动。除土地爷诞辰日外,其他活动的参与者都比较少,一般只有轮值户所在组别的部分村民参加。轮值户通过抽签产生,但每户只轮值一年,其他非轮值户则根据自愿原则参加。
这些活动虽然都与整个宗族有关,但从参与人数来看,它们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全村家户(做岁、上灯)、大部分家户(土地爷诞辰日)和小部分家户(其他节日)。通过这些经常性举办的节庆活动,村落内不同亲缘、不同居住地域的家户实现了关系互动,整个宗族被整合成一个内聚的团体。值得重视的是,在土地爷诞辰日邀请外村的朋友参加村落的活动,有助于加强宗族与周边村落的关系,拓宽了宗族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
在生产生活中,宗族活动和宗族组织中的房支范围更多地体现在婚丧喜庆的操办中。只要宗族中某一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动用较多的人员,与该家血缘关系最近的房亲与宗亲都会自动前来帮忙。这种帮忙纯属互助性质,没有任何报酬。在宗族内部,如果不考虑姻亲,亲属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是三四代以内的血亲,他们构成为一个互助性的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小房支”。但是,这个小房支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人丁繁衍不盛,家庭阄分、裂变的速度缓慢,小房支的范围会自动扩展,其可能的范围从上溯三四代,一直可以往上延伸,甚至可以追溯到整个福房或禄房这样的大房支。
在八井村畲族的福房内部,以该族清代富豪雷君恒为近祖(相对于开基祖雷安和而言)的血亲成员,就曾经构成这样一个关系密切的房支。在20世纪90年代初搬迁出“八扇房”之前,他们共同居住在这栋村中规模最大的房屋内,相互间关系密切,计有13户之多。在婚丧喜庆、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中,他们表现得好像是一个大家族或大家庭,而不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家户。在行政上隶属第二村民小组的禄房内部,由于人丁相对较少,在婚丧喜庆、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中,他们的亲属圈有时甚至扩大到整个禄房或整个第二村民小组。另外,正如上面所说的,近些年来,由于村内通婚,甚至同房通婚现象的增加,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也多搅和在一起,并相互帮忙。例如八井畲村原村支书雷信银是福房的,他们这个小房支中有些人与禄房的人通婚。所以,2002年农历七月初二他母亲去世时,除了他们自己的小房支的人都来参与和帮忙外,几乎整个第二村民小组的人,也即禄房的人几乎都前来帮助筹备和从事他母亲的葬礼,由于人多热闹,雷信银也觉得蛮有面子的。
第一节 宗族组织
八井村畲民以开基祖为近宗,构建了一个“宗族—房支—家族—家庭”的宗族体系。在这个血亲共同体中,由于没有福、禄两房共同的宗祠,同时由于没有族谱,人们的记忆又是有限的,所以福、禄两房在哪一代有共同的祖先,现在还不清楚。所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整个宗族更多地表现为是福、禄两个房分的组合。与此“虚拟”的宗族相比较,“房支”更是一个实在的实体,它以祠堂为中心,将数十上百户家庭维系在一起。八井村畲族分为福、禄两房,福房为长,禄房其次,其房支的开基祖现还不清楚。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八井行政村第一、第三村民小组的雷姓基本上都属福房,第二村民小组的雷姓则属于禄房;横埭村(属竹里行政村)的雷姓属于福房者为多,属于禄房者极少。八井新村与横埭村之间只隔着一条小溪,且同属福、禄两房,但彼此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由此可见居住地域对宗族内部关系有甚大影响。1990年以前,横埭、八井同属八井大队(1984年9月改为村),1990年行政区划变更后,横埭从八井村划出,与上竹里、下竹里同属竹里行政村,八井自然村与牛洋自然村同属八井行政村,并一直延续至今。
福房在人口数量上明显多于禄房,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往山脚平地搬迁之前,福房集中居住在两个区域,禄房则聚居在一个区域。虽区域不同,但彼此相隔实际不过咫尺。三个不同的住居区,以后便成为行政上划分村民小组(过去则为生产队)的主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们考虑到山脚平地交通的便利,遂陆续从半山腰的老村往下迁居,形成了今日福、禄两房杂居的居住格局。在八井畲村内,无论福、禄两房是分别聚居还是杂居,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始终都比较密切,长幼尊卑秩序井然。在我们所征集与抄录到的八井村畲族从清雍正年间到民国期间多达近300件的契约文书中,凡涉及族内典当借贷的,他们均以(堂)叔伯兄弟侄相称,族内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以前,福、禄两房各有一位房长,由房中辈数最高、年岁最长的人充任。房长是村落的自然领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每一房内,都专门留有几分田地,给房长耕种,收入归房长个人,也许是作为他为族众辛劳一年的一点补偿。房长辞世后,田地自动转让给新任房长。凡事关房内的一些公益性事情,如族谱的编撰和重修、祠堂的鼎建和修葺、祭祖的安排和实施、庙宇的修建和维护等,主要都由房长负责发起和主持。如遇有突发性事件,经众族人公议后,亦须得到房长的首肯。房内若出现严重纠纷,房长有义务进行仲裁。如果房与房之间发生纠纷,最终亦由两位房长出面调停。如果是和外村发生纠纷或冲突,则通常由房长等出面,会同当时最基层的政府人员如地保、铺长、乡长、保长等解决。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八井地区实行保甲制,八井畲村与牛洋村同属竹里保。保长由上面指派,最早是雷志东,两年后由雷坤珠接任。1940年,竹里保与小获保合并,保长为陈福福。①
1949年以后,宗族组织的政治、管理活动受到官方限制,房长在村落的领导角色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房长的产生所依据的只是辈分和年龄的原则,所以直到现在,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族人,仍然被雷姓族亲公认为所在房的房长,尽管事实上他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小。在福房,现在公认的房长是雷坤雨,他于1924年7月出生,2003年79岁;禄房房长是雷佺尧,他于1927年2月出生,今年76岁。二人虽同为房长,但遭遇迥异。雷坤雨无子嗣,由从起步镇护国村抱养的女儿雷伙妹招亲来延续香火,赘婿从连江县官坂招入,并改为雷姓,成为八井雷氏宗族的成员。他们为雷坤雨生了3个孙子,使雷坤雨延续香火的愿望和目的得以实现。在养女10多岁还未招亲时,雷坤雨急于解决香火继承的问题,不等养女招亲就先从竹里村抱养了1个孙子。然而,也许是因为过分溺爱和放纵,这位抱养来的孙子长大后却不争气,成天游手好闲、小偷小摸,被判3年劳教后,妻子虽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但也无法忍受他的行为而离婚改嫁到白塔乡去了。雷坤雨跟着养女一家生活,构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主干家庭,抱养来的孙子也分家另过。雷坤雨养女家纯以种植业为生计,因此家庭生活相对比较拮据。所以他经常衣衫褴褛,拄着根拐棍在村中闲荡。如果不是村民指认,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眼前这个瘦小的孤老头居然就是福房的房长。
雷佺尧的家庭情况与雷坤雨有点类似,但境况却是两样的。雷佺尧夫妇也没有亲生子女,他从罗源城关抱养了养女雷香桃(原姓吴),并通过养女招亲,招赘本村福房的雷信慈为“儿子”,雷信慈夫妇为雷佺尧夫妇生了2个孙子3个孙女。两个孙子与大孙女都已成家,大孙子雷可华有1男1女;二孙子有1女孩;大孙女有1男孩。所以从家庭香火繁衍的角度说,雷佺尧是儿孙绕膝,四世同堂,而且当了内外曾祖父。雷佺尧与雷坤雨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八井畲村中的“知识分子”。他年轻时跟随八井对面山上树楼村的法师蓝法吉(蓝得兴)学习闾山、茅山道法,在师父去世时,通过“奏名”仪式获得“法名”雷法莲,是八井畲村中有知识者。正因为这一机缘,雷佺尧比较注重其子孙的文化教育,亲自教孙子认字,并把他的法师知识传给了下代人。在他的关注下,他的养女雷香桃生于1955年,60年代受过小学教育,是当时村中读过小学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其大孙子雷可华生于1972年,高中毕业,2003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大孙女雷华妹(钗玉)1975年生,小学毕业。二孙子雷可良1977年生,初中毕业,并且是雷佺尧法师知识的继承人。二孙女雷伙玉生于1980年,中专毕业。三孙女雷金玉,1984年出生,现正在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就读。整个家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村里处于顶端,而且其儿子、孙子的家庭经济收入也都在村里属于中上等。自然,他也生活富足和无忧。在我们调查期间,身子骨硬朗的他,经常穿戴整洁,端坐在自家的新房前或村委会前的大榕树树阴下闭目养神,似乎在回忆昔日的往事。
无论过去或现在,房长的人选都必须是嫡生的,其他如抱养、过继或招亲的,即使辈分最高、年龄最长,也没有担任房长的资格。这类人家的子孙,要在抱养、过继、招亲后持续繁衍德的第三代,才有资格当房长。
福、禄两房都遵循共同的字行(字辈)原则,即同一辈分的人使用相同的一个字来起名,不同辈分则使用的字也不同。从第一代到第十七代,其字行顺序分别是:安—邦—民—飞—永—君—子—辅—朝—廷—乾—坤—志—信—可—知—贤。然而,在福房内,似乎自第十代即廷字辈开始,又确定了另一字行顺序:枝—大—向—章—传—世—德—恒—开。这是族人自述的一般性的字行顺序,但从其实际的运用来看,又经常出现变异现象。例如,雷辅铨的儿子本来是“朝”字辈,但除“朝泰”外,又有“枝相”、“枝迎”等名字,他们似乎与其他如“枝汤”等人共同构成了“枝”字辈。辅铨的孙子是“大”字辈,分别有大祚、大云、大马、大祯、大玉、大雨等人,按照字行原则,其曾孙应该是“向”字辈,但实际上又转回“乾”字辈,分别是“乾锐”、“乾金”、“乾标”、“乾炳”等。①再往后,则按“坤—志—信—可—知”的字行顺序起名。
在汉族社会中,字行的分衍,往往便意味着房支的裂变。但在八井村,似乎自明代至今,一直就存在福、禄两房,并未裂变产生出新的建有祠堂的房支。这大概就是他们不严格遵循字行规则的原因所在。即使在现代,情况也大致如此。如雷德明(1951年5月出生)属“德”字辈,他的儿孙的排行应该是“恒”和“开”,但实际上他的儿子取名叫雷知文(1976年7月出生),孙子取名叫雷贤镇(1999年10月出生)。在八井畲村,使用“恒”、“开”字行命名的人极为罕见。到目前为止,“贤”字辈年龄最大的已有24岁(雷贤坤,1978年3月出生,未婚),已达到婚育的年龄,所以他们急欲制定出新的字行,以便将这一区别世系的命名原则延续下去。
八井村畲族和汉族一样,遵循“父之党为宗族”的原则,族中女性的名字并不按字行命名,只在族谱上注明“女,××,配某地某人”。现在,除极少数年轻人外,绝大多数族人都仍然按照字行给子孙命名。依据各自的名字,族人能够轻而易举就辨别出彼此的辈分来。如此,不仅宗族内部的长幼秩序井然,而且宗族的世系序列也非常明确。
八井村畲民的名字均为复名,即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依字行确定,俗称“字头”,第二个字则自由选择,如“可”字辈起名“可良”、“可寿”、“可华”、“可木”等。在民国时期,族中男性除依字行确定的族名(谱名)外,还有字、号,并在族谱上予以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字、号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有号的人就更为罕见了。大多数族人还另有乳名,即孩提时代父母对他们的爱称,如“阿弟”、“阿根”、“细仔”等等。长大成人后,仍继续在族亲之间使用。但在正式场合,如入学注册、户籍登记等,这个名字则不再使用。
少数人还有法名。法名又叫“奏名”或“醮名”。在很多畲族族谱中,都可以看到法名的记录。据称,法名是畲民男女年届16岁经历一种类似于成年礼的仪式后所起的名字。这种仪式被称为“传师学师”或“作序头”、“传法录入”等。经过这种仪式的男女,被冠以“法名”,男性“法名”前都冠以“法”字,女性则后缀以“婆神”二字。①但是在八井畲村,只有具有法师(道士)的身份且师傅已过世的族人,才能取得法名。如禄房房长雷佺尧,其法名叫雷法莲。他曾经师从树楼村的蓝得兴(法名为蓝法吉)习法,师傅过世后取得法名。其孙子雷可良(1977年12月出生)跟随他学做道士,但因为他还健在,所以雷可良至今未取得法名,而只能用其祖父的法名做科仪。在八井畲村,也未曾发现女性有法名的。
家庭是宗族的最小单位,通过家庭的阄分、裂变,房支得以扩容,宗族力量也进一步增强。在八井村,一般结婚半年以后,新婚夫妇未及生育,就先行分家了,所以累世同居的现象极为少见。谚语也说:“娶一门媳妇,分一次家。”按照过去的习俗,分家通常由母舅主持,房内族亲参与评判。分配的财产为生产生活资料,如田园山场、房屋住所等。旧的炉灶归长子,其他儿子另起炉灶,这是取“传香火”之意。即使父母健在,一般也不留“养老田”,而是和未婚的儿子共同生活。如果儿子都已成家,父母的生活则由几个儿子共同供养。田产的分配,对长子有适当的倾斜,俗称“长子田”,但比例一般都较小。房屋的分配,如果仅有两子,根据“左昭右穆”的原则,则长子分左边厢房,次子分右边厢房,前厅与后厅则公用。现在的分家已比较简单,除非特殊情况,一般父母主持即可,并不专门恭请母舅出面,连族亲也不经常参与。对长子也没有明显的照顾,通常不分长幼,平均进行分配。待弟弟将来结婚成家时,为兄者再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考虑资助的额度。
在八井畲村,家庭之上,福、禄两个大房之下,实际上还存在着家族与小房支。例如上述所提及的雷佺尧和他的儿孙们的关系即为一例。雷佺尧家现已分家,他自己单过,形成一单身家庭;其养女及其丈夫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大孙子和其妻子和两个未婚的子女生活,这又形成为两个核心家庭;雷佺尧的老婆则与二孙子一家一起生活,形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主干家庭,而所有这些家庭都属于雷佺尧的派下。换言之,在雷佺尧的派下有四个家庭,即一个单身家庭,两个核心家庭和一个不完整的主干家庭。这些家庭的关系,即雷佺尧家族底下的几个家庭的关系。换句话说,大家庭分裂后形成的几个家庭,通常会在一个最近的共祖名下构成为一个家庭的联合体——家族。至于这种家族可以追溯到第几代,则要看其人口的多寡而定。人口少了,可能追溯得远些,人口多,则可能追溯得近些。而对于这种家族中的关系,八井畲民用“一家亲”来表述。
在家族之上,还存在着一些家族之上的小房支。这种小房支虽然没有明显的宗族象征物如专事于崇拜某位祖先的场所,但它确实存在,并经常在日常的仪式事务如婚礼、丧礼中体现出来。由于这种小房支没有明确的宗族象征物来体现,而且多以向上追溯到某代祖先来计算,所以我们以某某房支来叙说,可能要容易与清楚些。例如乾珍是八井雷姓的十一世祖之一,其派下现已繁衍到第十六代,现大约有十几个家庭(参见图6-1)。在这一层次上,他们属于人数较多的房支,彼此之间都比较亲近。其实这类房支的亲堂关系,是向上追溯的,如信银与信金为同胞兄弟,信银与信钦、信财为隔腹兄弟(公兄弟),他们同是乾谋房支的成员。信银、信钦与信开、信钗等虽是同辈的人,但他们要追溯到雷氏的六世祖时,才为同一房支的人。因为信银、信钦等为其六世祖的二儿子的派下,而信开、信钗等为其六世祖三儿子的派下,所以追到他们的六世祖,他们都属于同一房派。其他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此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八井畲村的畲民主要实行民族内部通婚,与周边如竹里、树楼等村,或起步、碧里、白塔乡等的雷、蓝姓畲族乡村互为婚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以后,由于三代以外的旁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受法律所保护,八井村原“祠堂内不能婚配”的传统习俗被打破,宗族内婚姻骤然增加,甚至房内婚姻也出现不少,但原则是五服以内不可婚。以雷可孝(1944年12月出生)为例,他有7个兄弟姐妹,除大哥雷可忠未婚先逝外,其余6个兄弟姐妹中有2个属宗族内婚配,占婚配总数的33%(参见图6-1)。在其第2代婚姻中,属于宗族内婚配的有9对,占婚配总数20对的45%。第3代已婚的只有2例,便有1例属宗族内婚配,所占比例暂时也是50%。雷可孝家的例子也许是一个特例,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八井畲村1949年以后宗族内部通婚渐趋增加的真实情况。
雷可孝的妻子雷翠云(1942年2月出生)原本姓蓝,父亲是邻近的起步镇人,母亲则是由八井畲村嫁出去的。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于是携4个子女回到八井村投靠娘家。以后再从竹里村蓝姓招了一门亲,并生了翠云最小的3个弟弟。她(他)们7个兄弟姐妹本来都姓蓝,但据说因为一时的疏忽,凡住居八井畲村的,其户籍上甚至身份证上的姓氏都变成了雷姓,包括他们的嫡系后代。对于这一“疏忽”,他们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表示希望给他们正名,恢复他们的“蓝”姓。无论如何,在翠云兄弟姐妹及其第2代的婚姻中,除翠云本人外,倒是没有一例属于村内通婚的(参见图6-2)。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
宗族内部大量通婚的结果,导致宗族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上,宗族是某一男性祖先的后代累世聚居所形成的一个血亲团体。在宗族组织中,核心成员是男性,它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进行大规模间接的宗族间的交换。根据交换的原则,族中的女性成员都不留在宗族内部,因此宗族的血缘主要通过男性的世系延续下去。但是在八井村畲族中,由于宗族内部通婚增多,导致很多女性成员留在宗族内部,并未进入交换的领域,从而使得宗族的血缘不仅通过男性成员,而且通过女性成员向下延续。由是,宗族遂演变成一个集血缘和姻缘于一体,既包括血亲又包括姻亲的社会组织。宗族内部的成员之间,也由单纯依靠血缘相联系,转变成为可能既有血缘上的联系,又有姻缘上的联系。宗亲之间的亲属关系,亦随之不仅是血亲关系,而且可能有姻亲关系。
宗族关系的这种变化,势必导致宗族内部在亲属态度和亲属行为上的相应变化。具体地说,这种变化可能是正负面兼具:一方面,它可能造成亲属称谓上的混乱,进而影响到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宗族内部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宗族成员从过去的生产生活中主要依靠数代范围内的血亲,扩展到可以依靠一定数量的姻亲。就前者而言,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也许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宗族可能会发展出一套相应的机制,来对这种后果进行匡正,可惜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未能就此展开更进一步的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另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通婚,使亲属圈的范围得以扩大,个人或家庭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增加。以雷可孝家为例,仅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的第二代就在八井村组建家庭13个(以结婚为标准),其妻雷(蓝)翠云的兄弟姐妹的第二代又在八井村组建家庭2个,加上第三代的2个,一共是17个。在这17个家庭中,计有10个家庭建立在宗族内通婚的基础之上。这样,即使假定所联姻的10个对象全都没有兄弟姐妹,他们至少也在村落中建立起总共达27户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占八井村总户数113户的1/4弱,①即约24%。如果考虑到宗族内的通婚对象多数必定有兄弟姐妹,这个比例实际上还要大,估计至少可以达到30%以上,即1:3强。如此庞大的一个血亲加姻亲关系网络在宗族体系中存在,不可避免地对宗族组织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村民就反映说,雷可孝家的亲属关系网络在近年来的村委会选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八井村宗族组织中,除了以血亲和姻亲为核心构筑的亲属关系网络外,还有一种被称为“人情谊会”的临时性互助组织,作为对亲属关系的补充。组织“人情谊会”的目的主要在于集中族众的经济力量,解决族人在结婚、建房、做小买卖等事情上所面临的资金周转问题。结会所涉及的金额一般不大,每一期少者200元,多者500元,通常为300元。利息为年息,通常是15%,理论上由全体会员共同享受。由于参加一个会所能获得的资金总额有限,所以有的人可能同时参加几个不同的会。“人情谊会”的会首(俗称“会头”)通常由召集和发起人充任,通常情况下,他也是最急需使用资金的人。参加“人情谊会”的成员一般为族中关系较好又有一定信誉的族亲,如果招募到足够的会员确实有困难,会首会考虑敦请外族中的亲戚或朋友参与。
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常见的“标会”不同,“人情谊会”在资金的使用上并不采取“投标”的方式,而是按照事先的约定依顺序使用。在结会之初,会首会出面协调,根据会员各自可预见的需要使用较大额资金的时间,确定好使用资金的先后顺序。“人情谊会”通常由10~12人组成,可以是月会,也可以是季会,分别按月份或季度上缴会资,每缴纳一次为一期。因为大多数村民的经济来源有限,所以月会事实上比较少见,更多见的是季会。但即便是季会,其实也并不经常按季度缴纳会资,而是一年中分为三次(即三期),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下半年为农作物收成的季节,会员上缴会资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另一方面,结婚、建房等大事也大多安排在下半年操办。
假如一个季会有12人参加,每期会资300元,其具体的运作办法是:第一年首期,会员每人向会首缴纳300元,共计3300元。第二期,每位会员应向会员甲缴纳300元,但因为会首已经使用过会资,所以他要另外缴纳15%共计45元的利息。这45元利息其他10人平分,每人4.5元,这样其他10人实际上只要缴纳295.5元就可以了。会员甲实际收取总会资3300元。第三期,会首和会员甲需向会员乙缴纳345元,其中属利息的90元由其余9人分享,每位会员10元,所以他们每人实际上只要缴纳290元即可。会员乙实际收到会资也是3300元。第二年的首期,会首、会员甲和会员乙分别向会员丙缴纳345元,利息部分共计135元属于其他8位会员,每人可分得约17元。这样,其他8位会员分别只要向会员丙缴纳283元即可。以后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一期,待到所有12位会员都收缴到会资后,此一轮的“人情谊会”方告结束。
虽然“人情谊会”中涉及高达15%的年利息,但因为这些利息基本上由会员共同分享,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属于宗族内部公益性的互助组织。况且,作为召集人和发起者的会首,他本人并未从中获取任何额外的利益。相反,因为他第一个使用会资,所以他为此付出的利息其实也比所有其他会员都要多。从实惠的角度来看,最后一个获取会资的会员无疑是得利最多者,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他所承担的意外风险也最大。这种互助性的民间组织,一方面有效地弥补了山区农村在资金来源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宗族内部族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其他汉族地区的影响,在八井村也出现了少数的“标会”组织,但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
第二节 宗族象征
祠堂、族谱是宗族的重要象征。在八井村畲族中,除祠堂、族谱外,还有祖杖、祖图、祖牌等宗族象征物。从表面来看,八井村畲民很重视祖先崇拜,其崇拜的对象包括远祖与近宗两部分,远祖是指“忠勇王盘瓠”(也称“龙麒”)、“立国侯雷巨祐”等盘瓠传说中的始祖,近宗则是八井村的始迁祖雷安居、雷安和兄弟及其以下的历代祖先。但是实际上,与汉族的祖先崇拜相信祖先会保佑他们子孙的简单态度不同,八井村畲民对祖先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远祖属于“神灵”的系统,近宗则属于“鬼灵”的系统。对于隐含在神话传说中的远祖,他们深知这些神灵与族人的关系十分遥远,并不会对他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任何实际影响,所以对它们表现为一种对“神”的崇拜,祭祀的目的也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族群上的认同。而对于以开基祖为代表的一系列近宗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视之为无法亲近的“鬼”,祭祀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或者只是为了讨好近宗的鬼灵,使它们不加害于自己的后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对于近宗的鬼灵表现出一种时时处处加以提防的心理。
这种提防心理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对待族谱、祖图、祖杖等宗族象征物以及与祖先相关的一切实物的态度上。他们相信,这些物品,只要是与祖先相关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神性,就会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可能的不利影响。显然,这是一种泛灵信仰,它使得八井村畲民对此类物品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只要不是自己非常熟悉的近亲,凡是他们用过或与他们有关的物品,都尽量不要去接触它,否则就可能给自己带来祸害。很明显地,在八井村畲民对于近宗的态度和他们的祖先崇拜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跨越的矛盾,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崇拜祖先,就势必相信祖先灵魂的庇佑,而不是对他们采取提防的态度。所以,我们宁可相信,祖先崇拜并非畲族信仰的原生形态,而是因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其祖先崇拜中隐含的这种矛盾。
根据这种泛灵信仰,与祖先密切关联的物品是不宜放在住宅内的,而只能集中放在祠堂中,或其他远离住宅的地方。例如,我们从村民雷可春处征集并抄录了一批从清代到民国期间的契约文书,新任村主任和他的太太就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们带到家中①,放在村委会办公室就可以了,否则他们“会害怕”(村主任太太的原话)。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和紧张心理,我们调查组要离开八井村时,才直接将这些契约文书和抄件从村委会带上了公共汽车。他们认为,如果将此类物品放置在住宅中,可能会给家人带来厄运。
祠堂:祠堂是宗族的最重要象征,通过在祠堂内定期举行的各种集体祭祀仪式,八井村畲民既实现了与远祖和近宗的心灵沟通,又达成了内部的团结和整合。祠堂既是神圣的场所,是祖先神灵的寄托所在,又是世俗的场所,是宗族聚会、训诫子弟和宣导宗法族规的所在。福房、禄房原各有自己的祠堂。福房祠堂位于祠堂厝,1934年曾经作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现几近于坍塌。禄房祠堂位于当中厝,于1946年被龙卷风刮倒,之后一直到几年前未能重建。近年来禄房在原地盖了间6平方米的三面墙小屋,内放有一些个人家中使用的“祖宗套”,但似乎也没听说有举行集体的公共祭祀仪式。由于没有了祠堂这种崇敬、祭祀祖先的场所,他们已多年未举行祭祖活动,就连祖杖、祖牌、祖图和族谱等宗族象征物,也已不见了踪影。重新修复祠堂,成为族人的一大心愿,尤其对人口占多数的福房族人而言。由于一些族人经济条件非常有限,虽经多年努力,至今未能如愿。部分村落精英至今仍在为此事四处奔波,在他们看来,重新整修祠堂和编撰族谱是当前增强宗族凝聚力的当务之急,也是衡量新一代精英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座祠堂于何时营建已不可考,但估计不晚于清代中叶。其依据有二:其一,八井村毗邻汉族村落罗厝里,即便以旧村论,两者相距也不过只有二三里地。从清代保留至今的契约文书来看,八井村与罗厝里甚至县城汉族之间的经济往来频繁,以至到解放初期,两村之间的山场田地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在经济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八井村畲族文化势必受到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仿照汉族宗族修建祠堂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二,在清代中期,八井村经济发达,甚至出现了像雷君恒这样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虽然族人都言之凿凿地解释,雷君恒幼年丧父母,由哥嫂抚养成人,18岁之前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只是在捡到1瓮金子之后才发迹,但他大量向周边汉族典买田地却是不争的史实。坐落于祠堂厝角落的两座规模宏大的“八扇房”,都是雷君恒自己出资兴建的,一座属其派下的长房,一座属二房、三房,在20世纪90年代迁出之前,居住着9户和13户人家,其中还有几间房专门作为房中子弟修习功课的书院。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兴修祠堂的可能性应该最大。
当然,按照一般的惯例,宗族的祠堂不太可能由某一人修建,但诸如雷君恒等族中财力雄厚的富户,一定是祠堂兴建的主要倡议人和资金的捐助者。其他一般的族人,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总之,祠堂的兴建既是宗族经济实力的体现,又是宗族成员团结协作的结果。在形制上,八井村畲族祠堂与周边的汉族祠堂基本类同,但是它里面所存放的宗族象征物无疑要比周边的汉族祠堂多,包括族谱、祖杖、祖图、祖牌、香炉、楹联等。这6件象征物,通常被称为畲族的“镇祠之宝”。八井村畲族对祠堂的内外环境极其重视,不仅祠堂内的神龛、几案要保持洁净,就连祠堂前后的地块都要勤加打扫。祠堂有“值祭”,由族中各户依次承担,除负责每月初一、十五日的焚香点烛外,就是保证祠堂的内外整洁。根据族规,如果发现祠堂不洁净,“值祭”必须受罚,处罚方式是继续轮值。
祠堂内供奉着自始迁祖以下的历代先祖的“神主”牌位,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一日为房族的祭祖日期。一般人死后便立一牌位,每年的忌日在家中祭祀,待三四代之后即放入祠堂,进入祖先的灵魂系统。进神主牌位入祠,每人缴纳240文。因为现在祠堂已废,所以祖先牌位都是和本境的各类神灵的神位或神像一道,放置在住宅中厅堂正中的神龛上。牌位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不具体书写姓名的远祖近宗牌位,上书“冯翊郡雷
家堂上历代远近宗亲香位”等,这种牌位,当地畲民称之为“祖宗套”;另一类是去世不久者的个人牌位,上书“显考雷公××之神主香位”或“显考××雷府孺人之神主香位”。有的则是将夫妇合写在一起的牌位,上一般书写“显考雷公××妣×氏孺人之神主香位”。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家人需焚香点烛。
族谱:族谱是宗族谱系的物化形式,其撰修时间应该与祠堂的鼎建大体同步。在八井村畲民看来,编修族谱、兴建祠堂和祭拜祖宗是宗族中重要的三件大事。其中,编修族谱又是重中之重,因为族谱用文字的形式,追溯了宗族的远古来源,历数了开基祖为宗族的生存与繁衍所付出的艰辛。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谱系的文字记载,每一个族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超越时空的障碍,把个人与其他族亲、与历代先祖联结在一起。对于个人而言,由此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对于宗族而言,由此产生一种血缘上的认同。这种血缘的认同再通过地缘的聚居,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内聚力,从而构成为宗族组织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当然,即使在没有族谱的情况下,族人也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宗族谱系往后延续,但这种方式毕竟没有谱牒记载那样持久、那样明确。
根据鼎建祠堂的时间来推测,八井村族谱编修的时间应该也是在清代中期。编修族谱的事宜由房长主持,配以若干族人主办。各家提供本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子嗣婚嫁状况和墓葬建造时间、方位等,这些内容称为“家状”。修谱先生根据各家提供的“家状”,构拟出宗族繁衍的世系图。当地人也认为,修谱者如果没有把族中的所有人的关系记录清楚,以后那些没上谱者的阴魂会找他的麻烦,使他不得安宁。谱内世讳的确立按“排字世项”的原则进行,载于族谱中的正式名字称为“谱名”,由“讳名(世名)、字、行第”三者组成,它表明族人在族中的世属和排行。人死以后,牌位和墓碑上用的都是谱名。如前所述,现今的八井村民并不遵循行第的原则,而是依世代所属字行,第一个字按字行规则取用,如“可”、“知”、“贤”等,第二个字则由父母随意确定,只要尽量不与其他族人重复便可。
八井村禄房的祠堂倒塌得早,族谱在多年前就不见了。福房的族谱原来一直就放置在破漏的祠堂内,大约七八年前,被一个小偷连同祠堂内的其他一些物品一起偷走,也不知去向了。
以前,每年农历的七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族谱被从祠堂内的神龛上拿下来,放在厅堂正中的几案上,供众族亲展阅。据看过族谱的族人回忆,像其他畲族族谱一样,福房族谱中有“谱序”、“凡例”、“敕书姓氏封”、“得赐三姓源流纪”、“龙首师杖志”、“历朝封赠”、“差扰”、“高辛驸马龙公墓图”、“立国侯祐像赞”、“字行”等内容,这些被称为“谱头”。在“谱头”之后,是福房雷姓的世系图,包括分居在横埭等地的宗亲。
祖杖:祖杖又称“龙首师杖”或“法杖”,是八井村畲族显示远祖权威的象征物。平时和祖图、族谱一起存放于祠堂正厅上方左右两侧的木柜中,不轻易示人。举行祭祀仪式时,向族众展示,展示完毕即放回原处。祖杖长约四尺,头部雕刻成龙头状,今已不存。距离八井村仅数里的树楼村蓝姓族谱中有《龙首师杖志》,其记曰:“按盘瓠王生于帝喾高辛氏四十五年五月初五日,时至帝尧陶唐氏廿一年六月廿七日,盘瓠王游山伏猎,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登树岔而卒。十七日得尸而归,同朝奉上。帝思功臣生既非怀于人胎,死复不归乎中土,命将士将树砍回,召青州范氏刻盘瓠王颜像,名曰‘师杖’,谥为忠勇王,每朔望致祭。四月初八日丑时葬于凤凰山,坐卯向酉,立有石人石马石麒麟。为记。”①
祖图:祖图又称“太公图”或“长联”,是关于盘瓠传说的实物资料,于每年的正月初五日“开年驾”(表示新年结束,要开始生产活动了)时,横挂在祠堂正厅的墙壁上,向族众展示一天,意在向族人宣导远祖的业绩。翌日清晨,便小心地珍藏起来。据族中老者介绍,八井村畲族祖图为一条状横幅长卷,长1米左右,底为麻布,上面浓墨重彩,图文并茂,描绘了盘瓠变身、征番有功、招驸马、受封、狩猎等有关盘瓠传说的历史场景。虽族人爱护有加,惜因祠堂毁损,早已不知去向。
祖牌:祖牌又称“龙牌”,系祖先的牌位,一般一位祖先就有一个祖牌。祖牌为木制品,上雕以纹饰,并用文字注明系哪位祖先的牌位。祖牌放置于祠堂正座的祖龛内,其雕制和进龛都要选择吉日吉时,不得马虎。凡属众家的牌位由祠堂出资修造,属各家的牌位由各家自行修造,由此导致祖龛内的祖牌虽造型类似,但装饰不一。有的祖牌甚至镶有金箔,做工也十分精致、考究。现在,因祠堂无法放置,祖牌已被家中的牌位所取代。在村民雷可孝家中,我们发现其为未婚先逝的大哥设立的一块牌位,上书“永言孝思显考雷可忠历代远近宗亲香位曾孙雷贤斌祀”。经询问得知,雷可斌尚未成年,系雷可孝的孙子,名义上过继给伯祖雷可忠。但既是过继,又为何在辈分上降了一辈,由“孙”变成“曾孙”?我们不得而知。
香炉:香炉为铜制,代表着香火,所以受到八井村畲民的格外重视。它既是祠堂内举行祭祀仪式时的必需物,也是八井畲村宗族的象征物之一。
楹联:楹联由族中或族外的儒士撰写,在各地祠堂内均可见。它以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宗族的历史和人文。和周边的汉族相比较,八井村畲族的楹联其特殊性在于,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惟内容始终保持不变。遗憾的是,在八井畲村福房祠堂内,我们连一对楹联也没有找到,相反,倒是有一些零星的“文革”时期的标语和已故领袖人物的画像。
第三节 宗族活动
宗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其团体性体现在与全体族众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中,反过来,通过这一系列与全体族众相关的活动,宗族组织的团体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活动可以是有组织的,如祭祖、宗教性集会,也可以是自发进行的,如生产中的合作、生活中的互助等。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主要以地域为依据,所以在乡村一级特别是村级行政组织中,行政区划与宗族组织出现了部分重叠。特别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生产活动的组织往往是以房份为单位,所以出现了行政村与宗族、村民小组与房支难以分割的状况。以八井畲村为例,八井行政村包括八井和牛洋两个自然村,它们同属一个宗族。在八井行政村内,第二村民小组与禄房对应,第一、三村民小组分别与福房的两个房支相对应。由于行政区划与宗族组织的重叠,现阶段很多宗族组织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活动的形式来举行。
每年农历七月十一日的祭祖仪式,曾经是八井村雷姓宗族中最为隆重的宗族活动。祭祖由族中各户轮流主办,从七月一日起,就开始拟定祭祖祝文,用为祭祖时诵读。祭祖时,需陈列祖图、祖杖、族谱等。主祭人为族中房长,陪祭人为每家家长,限20岁以上成丁,无男则女代。祭祖时有通赞2名、引赞2名、读祝文者2名、司众钱1名、司箔1名,均为族中有名望和地位者。八井村没有祭田,祭祖的费用由各户平均分担。捐立田租1000斤者,公立禄位,永垂后裔。捐钱100两修建祠堂者,也有禄位。结婚要纳喜钱100文,生男孩要纳喜钱60文,祭祖时交纳,作为祭祖经费。祭祖之前,要清扫祠堂、洗涤祭具、陈设器皿、备足祭品。祭品不作定例,可以随时斟酌,但不得用不洁或减价的物品,否则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祭祖之日,午夜子时鸣铳一响,族人即便起床,盥洗准备;丑时鸣铳两响,主祭和陪祭盛服入祠;寅时鸣铳三响,族人毕集,宣读祭文,集体致祭。礼毕,族众会餐,俗称“饮祭”。①在喧哗的聚餐中,宗亲之间的亲情得以提升。
时至今日,虽然全族性的祭祖仪式暂时消失了,但家族的墓祭仪式仍然保留下来。每年清明时节和白露节气,同一家族的族亲带上祭品,到祖先的坟墓前祭扫。墓祭由家族中的各户轮流主办,与祠堂祭祖相比,祭品比较简单,一般也不举行会餐。近些年来,墓祭的对象已逐渐简化为高祖及其以下的祖先。村民雷可寿解释说,因为历年墓祭都没有给族人带来明显的好运,所以渐渐地就放弃不祭了。例如,雷君恒及其裔孙雷辅铨的坟墓占地都不小,墓制也非常奢华,但现在墓碑上都布满了青苔,周边杂草丛生,甚至长出了小树,以至我们要带上镰刀、木棍,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来到墓前,勉强看清碑文。很明显,这两座墓都已多年未祭扫,况且雷君恒还曾经是清代中期族中的豪富。
除祠祭、墓祭外,还有家祭。祠祭仅在七月十一日及其他重大节日时举行,墓祭集中于清明节和白露,家祭则在平时和一般节日于家中进行。三者之中,祠祭最为隆重,家祭最为简单。家祭通常由家中妇女操办,陈设些许蔬果茶品,焚香点烛就可以了。虽然家祭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是私人性的,与宗族性的祠堂祭祖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也有别于家族性的墓祭。实际上,三者分别代表了宗族、家族和家户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空间。
由于宗族性祠祭活动的消失、家族性墓祭活动的淡化及其他一些可能的集体活动(如赛歌)的失却,八井村雷姓宗族组织的活动已浓缩在一些重大的节庆、婚丧喜事的操办和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中。就重大节庆而言,“做岁”、“上灯”及其他6个节日是宗族活动得以开展的主要机会和场合。
做岁:正月初一或十五日,以分组为单位,由上一年度轮耕“岁田”的家户,从“岁田”的收成中支出约200斤稻谷,到白马宫致祭,晚上分组成员在白马宫会餐,就餐者通常为家中的男性长者。“岁田”约有2亩,实行生产责任时专门划拨出来,多为山田,可耕种一季,亩产糯谷约300斤,杂交稻谷500多斤。每个村民小组又分成2~3个分组,每组7~8户至10余户不等,视总户数多少而定。每个分组的家户数实际上是不固定的,因为随着分组成员家庭的析分,每组的户数也在相应增加。但显然,这种户数的增长是缓慢的。据雷可寿称,他所在的分组属第一村民小组,共有16户,至今已轮值至第二轮末,他家是最后一个轮值户。轮值户的确定,系由抽签产生。在民国时期,则依商议而定。在第三村民小组内,由于户数相对较少,所以他们通常不再分组。前一年有喜事的村民,如盖房、娶媳妇、生育(无论男女)等,会在聚餐时专门给大家散烟。烟的质量和数量视各家经济情况而定,或2~3元一包,或7~8元一包,少的人均散发1~2支,多的每人一包。
从常理上来判断,“做岁”应该是在正月初一日,而不应该也包括正月十五日,因为“岁”字在八井村畲族的语言中也是“年”的意思。在一份年代大约为清代中后期的文档中,有“雷子英,九分正;辅登,应乙分五厘;辅和,应乙分五厘,拨元宵赛”的记录。我们据此初步判断,至少在清代期间,八井村畲族曾经有举办“元宵赛”的习俗。而且,可能还有专门用于举办“元宵赛”的“赛田”。在一份有关“赛田”的买卖合同中,甚至还注明有“大小鼓全堂,又碗壹付”,而这些物件通常是集体聚餐所需的。该合同如下:
立卖断赛田根约雷大会自己手置有赛田壹号,坐属拜井里小获地方,土名俗叫仔田壹号,载租谷肆百贰拾斤大称。今因无钱乏用,即将此佃田托中到引断根于堂兄大云处为业。三面言议,得出断价钱壹仟肆百文。其钱立断之日同中亲手收讫,其田即付钱主耕作纳租。其田价足心愿,葛藤以了,日后子孙不得言购言赎,亦不敢生端枝节之理。但此田是(大)会自己之口,与亲堂伯叔侄无干,日前并未曾重张典当他人财物。倘有不明,系是(大)会出头抵当,不涉钱主之事。两家情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卖断赛田根约壹纸为照。
又及:口大小鼓全堂,又碗壹付,再照。
中见代字钱陆拾四文,再照。
中见代字 堂侄 向宾
光绪五年贰月 日立卖断赛田根约 雷大会
该合同留给我们的疑问是:既是为“元宵赛”所置的“赛田”,又为何是属于个人的,且转让给了族人?故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断定所谓“赛田”就是专门为“元宵赛”而置,更无法探明“元宵赛”的具体运作情形。
上灯:正月十一至十八日,以分组为单位,由轮值户出面,向其他家户每户收取10到20元钱,作为祭祀和会餐的开支。以前,以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组织。考虑到户数众多,组织不易,现在才改由在村民小组的范围内分组进行。具体的时间安排是:第一村民小组,十一至十三日;第二村民小组,十四至十六日;第三村民小组,十七至十八日。日期有长短之别,主要原因是每个村民小组的户数不等。第三村民小组家户最少,共25户,第一村民小组的家户数最多,共43户,第二村民小组40户。在白马宫内,可同时容纳约12桌共120左右人就餐。重要的是,各分组中的家户构成,与“做岁”时进行分组的家户构成并不相同,虽然它们也有部分重叠。
无论是在“做岁”或是“上灯”的活动中,从表面来看,家户之间的这种组合都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但事实上,这种组合都遵循一定的地域原则,只不过这种地域原则被掩盖在村民小组的行政区划之下,因为在八井村和在其他行政村一样,村民小组的划分大体上是以居住区域为标准的。民国时期此两项活动开展的情况,更印证了这一构成原则。在民国时期,八井村有“四境”之分,分别对应着八井村四个大的居住区域。在举行“做岁”或“上灯”活动时,是以一“境”作为单位的。那时,每一境也都有自己公共的“岁田”,境内实行轮值耕种,收成的一部分(也是约200斤稻谷)作为活动的开支。作为轮值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部分来源,那时的“岁田”得到村民的重视。他们辛勤耕耘,力争有一个好的收成。而现在,“岁田”经常被抛荒,活动开支改由轮值户自己掏钱。
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日。各地畲族均重视“二月二”,但说法不一,有的地方认为是“会亲节”,有的地方认为是“神节”甚或“种竹日”。①八井村畲民认为,土地公能保佑生产不受灾害,给村民带来财运。在祭拜土地公及随后的会餐中,“做岁”或“上灯”活动中的分组原则均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自由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的对象通常为自己的朋友或亲戚,基本上是本族范围内的,也可以是外村的,唯人数以10~12人即一桌为限。所需经费由大家共同捐资,多少由各人自己决定,而不必是平均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一般会多出资一些。有理由相信,此次仪式性活动为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提供了一次展示财力的机会,而经济实力是获得和保持在村落中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每年的土地公诞辰日,这样的临时性组合都会出现好多个。
做岁、上灯、祭拜土地公等这一系列民俗活动,无疑可视为宗族活动之一种,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宗族活动的延伸和补充。因为在八井畲村,属于整个宗族的大宗祠未能建构起来,所以村庙建筑白马宫,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宗族活动的场所。白马宫属宗教建筑,修建在村落的古村口,门前的小路是以前进出村落的要道,供奉的神祇主要是当境神主白马王,其次是临水夫人、五显大帝和土地公。因为全村性的活动多在白马宫内举行,所以它们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与地方宗教信仰有割不断的联系。在周边的汉族村落如罗厝里、小获等,虽然也都有村庙白马宫,但仅限于神灵诞辰日的各家祭祀,而没有像八井村这样的集体性聚餐活动。
除做岁、上灯这两次在新年期间举行的活动外,在白马宫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共有6次。为了确保这6次活动都能举行,村落约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别负责:第一村民小组,三月十三日白马王生日和八月十三日左、右将爷生日;第二村民小组,五月五日端午节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冬至;第三村民小组,二月二日土地公诞辰和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每个村民小组内,又各分成两个组,分别负责一次活动。除土地爷诞辰日外,其他活动的参与者都比较少,一般只有轮值户所在组别的部分村民参加。轮值户通过抽签产生,但每户只轮值一年,其他非轮值户则根据自愿原则参加。
这些活动虽然都与整个宗族有关,但从参与人数来看,它们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全村家户(做岁、上灯)、大部分家户(土地爷诞辰日)和小部分家户(其他节日)。通过这些经常性举办的节庆活动,村落内不同亲缘、不同居住地域的家户实现了关系互动,整个宗族被整合成一个内聚的团体。值得重视的是,在土地爷诞辰日邀请外村的朋友参加村落的活动,有助于加强宗族与周边村落的关系,拓宽了宗族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
在生产生活中,宗族活动和宗族组织中的房支范围更多地体现在婚丧喜庆的操办中。只要宗族中某一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动用较多的人员,与该家血缘关系最近的房亲与宗亲都会自动前来帮忙。这种帮忙纯属互助性质,没有任何报酬。在宗族内部,如果不考虑姻亲,亲属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是三四代以内的血亲,他们构成为一个互助性的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小房支”。但是,这个小房支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人丁繁衍不盛,家庭阄分、裂变的速度缓慢,小房支的范围会自动扩展,其可能的范围从上溯三四代,一直可以往上延伸,甚至可以追溯到整个福房或禄房这样的大房支。
在八井村畲族的福房内部,以该族清代富豪雷君恒为近祖(相对于开基祖雷安和而言)的血亲成员,就曾经构成这样一个关系密切的房支。在20世纪90年代初搬迁出“八扇房”之前,他们共同居住在这栋村中规模最大的房屋内,相互间关系密切,计有13户之多。在婚丧喜庆、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中,他们表现得好像是一个大家族或大家庭,而不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家户。在行政上隶属第二村民小组的禄房内部,由于人丁相对较少,在婚丧喜庆、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中,他们的亲属圈有时甚至扩大到整个禄房或整个第二村民小组。另外,正如上面所说的,近些年来,由于村内通婚,甚至同房通婚现象的增加,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也多搅和在一起,并相互帮忙。例如八井畲村原村支书雷信银是福房的,他们这个小房支中有些人与禄房的人通婚。所以,2002年农历七月初二他母亲去世时,除了他们自己的小房支的人都来参与和帮忙外,几乎整个第二村民小组的人,也即禄房的人几乎都前来帮助筹备和从事他母亲的葬礼,由于人多热闹,雷信银也觉得蛮有面子的。
附注
①1998年新修《罗源县志》载:据1990年的统计,罗源县畲族有28个支派,其中雷氏13个,蓝氏12个,钟氏3个。
②《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出版,889页。
① 《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1页。
①资料来源:雷辅铨墓碑文,上载:“清显考辅铨雷公、妣蓝氏孺人,附次男朝泰、次媳蓝氏,阳男枝相、枝迎,孙大祚、大云、大马、大祯、大玉、大雨,(重孙)乾锐、乾金、乾标、乾炳,咸丰丙辰年桂月吉旦立。”
①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0页。
① 关于八井村的家户数量,户籍登记与实际的家庭数有出入,此处以实际的家庭为准。(参见第四章人口)
①在八井村调查期间,承蒙村主任的好意,我们一行6人都住在他的新宅中,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此,也顺便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①载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树楼村《蓝姓族谱》。
①参见《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31页。
①《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年,190~19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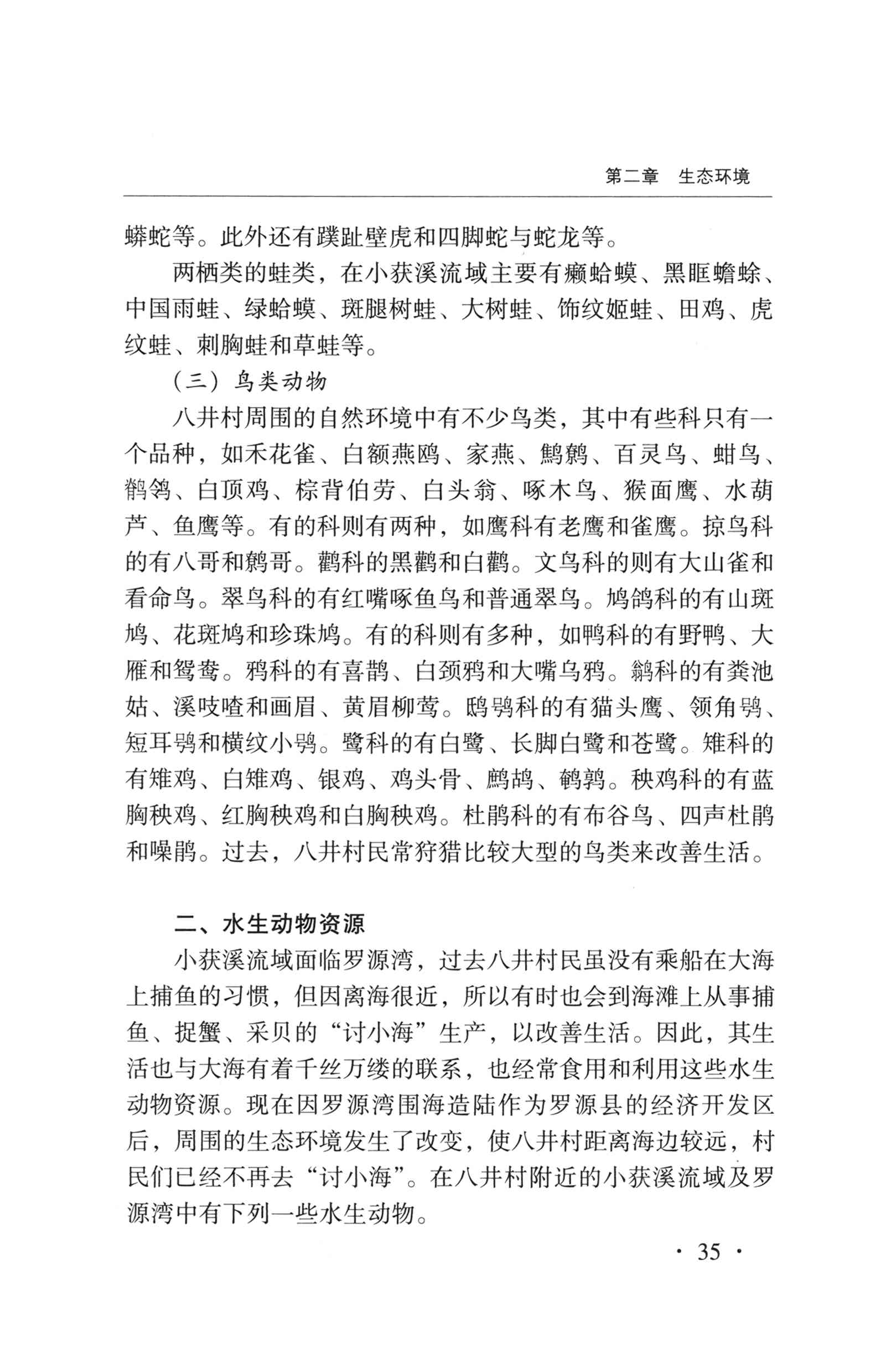
《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对福建省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的调查,依次介绍了其概况与历史、生态环境、经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管理、法律、民居建筑、风俗习惯、口传文化、教育等。
阅读
相关地名
八井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