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80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14 |
| 页码: | 91-104 |
| 摘要: | 本文主要探讨了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和“畲”汉边界的形成。 |
| 关键词: | 畲族 来源 多源性 |
内容
族群边界既是自然生态、族群迁徙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建构、文化再造的结果。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贴上族群标签,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他者”的建构来强化对“自我”的认同,从而实现资源的争夺①。宋代时期,“畲”汉边界形成,这种边界的划定,是“畲”汉人群集体意识的结果。
一、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在唐宋以后,关于南方地区“莫徭”“峒蛮”“蛮僚”的记载日益频繁见诸史料,这既体现华夏族对“他者”认识的加深,同时也是说明南方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一些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上,如谢重光先生指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已经形成了福佬族群。②与中原汉人同时南迁的还有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这些族群“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③,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南方地区汉人与非汉人群的互动,既有族群间的合作,又有族群间的冲突与对抗,唐宋的一些文献记载说明了这点。如《资治通鉴》记载道:“(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甚至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④
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蛮夷”就是畲族先民⑤,滨海蛮夷则应为“蜑民”。这些“洞蛮”以兵和船的形式,为以王潮为代表的汉族势力提供了帮助。再如景福二年(893年),汀州盘瓠蛮酋“钟全慕举籍听命,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潮乃尽有五州之地。”①则说明了一些蛮夷归顺了朝廷,成为中央王朝治理地方的合作者。这种合作间接地说明了南方汉族势力的逐渐增强。
南方汉族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当地汉人对祖居地的解释和建构上《太平寰宇记》在记载“永泰县”时称:“《晋安记》:‘东晋永嘉之乱,渡江衣冠士族多依于此,以求安堵’。当此之时必有县,后人或更改,图未甚详悉。”②
乐史根据《晋安记》的记载,对“晋人衣冠南渡”这一历史事实做出推论,认为当时南迁汉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建立州县,只不过因为建置沿革变迁或记载不详而未能使县名存留于世。这种说法在宋代以后的南方地区颇为流行。“衣冠南渡”成为一种当地汉人祖源历史记忆,并作为文本在福建等地的文献中出现如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代路振的《九国志》称:“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③《八闽通志》卷之三《地理》风俗引《建安志》称建宁府:“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云云。”④
王明珂先生指出,一定的历史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而这种社会情境又与当时的历史心性息息相关。⑤因此我们认为,隋唐以后南方蛮族记载的增多以及汉人祖源地传说的建构,均是在南方地区汉人势力崛起这种社会情境中产生的。
唐宋或更早时期,华南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边缘性不仅反映在政治地理上,更反映在文化阶序上。随着汉族势力在南方地区的增强,处于帝国边缘地区的南迁汉族或当地汉族土著为了提升自己的族群身份,往往对本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上述所举例子说明,当地汉人希望通过回忆或者建构类似“衣冠南渡”的历史来增强华夏认同,从而提升本地汉人的族群地位,并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汉人心目中,早在汉晋时期,本族群的祖先就来到包括福建在内广大南方地区,这进一步证明本地汉人在此地开发、经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汉人增强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两个手段:
一是建构自己的“汉人”身份。如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地方土著积极向汉族或中原王朝靠拢,如积极协助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治机构,“请书版籍”,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后,意味着族群从“化外”向“化内”转变;再者就是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
二是与“蛮夷”划清界限。如在宋代开始,陈元光家族被描述为来自光州固始,且受命于朝廷“平蛮”的中原正统家族。一些非陈姓的汉人,通过建构本族为陈元光“部属”的历史记忆,说明本族与陈元光家族一样,均是中原正统身份。这种历史记忆间接反映了宋明以后,闽南等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通过将本族群与当地蛮夷截然区分,从而建构其本族非蛮的历史逻辑。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献对陈元光记载甚多,陈元光因此被认为是开发漳州的重要人物,以致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开漳圣王,成为流行于闽台诸省重要神明。而实际上,陈元光在唐代的形象与后世的形象相差较大,其中经历了一个历史人物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与闽南地区的汉族认同有特别大关系。唐代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目前所能发现的关于陈元光事迹的文献记载为张鷟的《朝野佥载》,其文称:“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①
作者张鷟的生卒年不详,但生活年代与陈元光相差不远,其所载的关于陈元光内容,纵使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至少反映了时人对陈元光其中一个印象的理解。作者将陈元光这种残暴的性格特征与岭南首领相联系,反映的是北方汉人对南方土著的印象。宋代《太平广记》在引用以上史料时,特意将其置于“酷暴”一节之中。②可以说,唐代时期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且较多为负面形象。从宋代起,漳州地区开始流传陈元光平贼立功的传说,并建庙对其奉祀。宋代漳州令吕璹有诗写道:“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族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③
前文已经说明,宋代时期福建等南方地区汉族意识逐渐增强,塑造陈元光平蛮的形象就是将本族群与“蛮”相区别,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这应该是
陈元光形象塑造的滥觞。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方志、族谱不断塑造陈元光的光辉事迹①,兹不赘述。
由此可见,从唐到宋,及至明清,陈元光的形象逐渐丰满,并以将军、儒士、神明等形象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不断层累、“枝叶其说”的历史建构过程。这种建构的力量来源于闽南等地汉人文化认同的需要。
苏永前通过人类学视野对陈元光“开漳”传说进行分析,他认为该传说的叙事主体为闽南地区中原移民,而传说的产生与传播则是该族群文化认同的主观结果。这种认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圣化”和“神化”,另一方面是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②由此可见,将本族与“蛮夷”区分开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本族群的纯正中原血统身份,这是一种主观认同的表现。
除了陈元光家族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宁化巫罗俊家族。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③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熊修所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④。而巫罗俊的事迹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清代王捷南称:“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①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做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传说本质也同陈元光传说一样,都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②
二、标签化与作为族群文化特征的“畲”
刘志伟通过对清代以后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和民田区研究后发现:二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土地自然形态的差别,实际上是在地方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甚至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记。两个区域之间,除了自然形态的差异外,更存在一种独特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③就此而言,畲田经济与农耕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区别,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阶序、族群格局。确切地说,在华夏民族观念中,从事畲田的族群是不受王化的“非我”族群,而实行农业的则是王朝子民,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华夷之别”。将某一类族群归为“异类”,意味着其无法与华夏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享有同等地位。在唐宋时期,“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充当了“异类称呼”的角色,这种贴标签的过程是伴随着华夏族的族群认知一起进行的。
在隋唐以前,由于南方开发缓慢,作为一种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等词语常用于表示一个地区经济落后、蛮荒化外、教化不及的状态。如《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④《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⑤《汉书·地理志》又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⑥,《盐铁论·通有》云:“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①《晋书·食货志》:“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②《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赎物,以裨国用。”③有的记载甚至直接将“火耕”“水耨”等耕作方式认为是蛮獠的习俗,如《唐大诏令集》载:“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④按照文中意思,“居人”相对于“蛮獠”,应该是汉人;“火耕水耨”是“蛮獠”的风俗,汉人在耕作方式上被同化了。
有的甚至引用春秋以前的休闲耕作制度来形容一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如万历《古田县志》记载如下。
林谞《闽中记》:开元二十八年,都督李亚丘会溪峒逋民刘疆辈千余计归命向化,乃状其事以闻。越明年四月二日,命下允俞而始立邑,当环峰复嶂间,平陆三十五里,版垣墉高丈许,步三百周。树室辟户,张官置吏,子男之邦,周宏远规。先是,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⑤
林谞《闽中记》修于唐大中年间,是福州较早的一部方志,已散佚,林谞事迹见诸《八闽通志》⑥。林谞用“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来解释古田县名的由来,其中“田畯”“敷菑”“疆亩”的典故出自《诗经》《尚书》等文献,⑦均是春秋战国以前休闲耕作制生产及其管理的专用词语。林谞用典的寓意:或者是好古,用典溯及三代,言辞溢美;或者用以说明古田设县之前,该地“溪峒逋民”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可见,主流文化圈时常将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与当地的农业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有一部分记载并不都符合史实,显示的是主流文化圈在“南北问题”上的文化偏见。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与“畬”有关的文学作品,并有许多与山区的非汉民族联系在一起,除了一部分写实、猎奇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畬”来区别族群,如上述所说的莫徭、蛮、獠等。唐宋时期“畬田”农业与一些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的高度重合,原本就带有“华夷有别”文化偏见的汉人将“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类族群身上。
如前所述,唐宋畲田区域逐渐缩小,刚好一些南方山林地带的非汉民族仍保存着这种古代农耕残存形态。如唐代刘禹锡之《莫猺蛮子诗》称莫徭实行刀耕火种,该诗写道: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春。夜渡千仭溪,含沙不能射。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麕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①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一些被称为犵狑、犵獠、犵榄、山猺等非汉族群刀耕火种的习性:“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㺏,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②
畲已然成为非汉族群一种特征,因此也为后来将一部分实施刀耕火种的族群称为“畲”埋下铺垫。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志》中曾对畲民来源进行考证,他说:“考畲民本山越孑遗……畲民山居,亦称山輋或山人……宋谓之畲或輋,以其民居山谷烧田为生,故以此名之。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盖山越也称山民,后人专以山民呼之,寖失越名,以其居于近山之地,遂相呼曰輋。”③饶先生认为,畲民可能源于山越,只不过因为“山居”或“烧田”而被称为“輋”或“畲”,所谓“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言下之意,“輋”和“畲”均为其他族群(主要是汉人)对“山越”的他称。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与畲民有关的诸多称谓,如明清时期“棚民”“菁民”等,这些称谓的出现,与当时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族群标签被贴上后,一些经济方式、经济作物也逐渐与该族群发生联系,这是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如出产于广东、福建等地区的稜(菱)禾,在宋代时并未完全与畲族有联系。《方舆胜览》对梅州程乡的菱禾进行了记载:“土产菱米,不知种之所自出,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粝。”①
而到了明清以后,稜禾(菱禾)均与畲族等非汉民族发生了联系,如明嘉靖《惠安县志》:“畬稻种出獠蛮,必深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②清代《临汀汇考》称稜禾又叫畲米,分为两种,“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两种,四月种九月收,六月八月雨泽和则熟。.”③清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称:“畬稻,种出獠蛮,晋江四十七都多种之。”④再如刀耕火种也打上了族群的烙印,《广东通志》:“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⑤
畲的最初形态除了经济形态,还有与“峒”有相类似的聚落或地名特征。在宋元,畲也被视为地区或聚落的名称,“畲”与“峒”一样,都有一个从“聚落”“地名”到“族群”含义转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转化有时候是可逆的,即:住在“畲洞”里的人被称为“畲民”,而畲民聚居的地方可能又被称为“畲洞”。实际上,南方的许多族群名称都经历了这种转化过程,如瑶,一般认为是由“莫徭”转化而来,因“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⑥再如僚(或獠),按郭璞的《史记·集解》解释为:“僚,猎也。”《索隐》引《尔雅》又云:“霄猎曰僚”。⑦清代梁绍献《南海县志》:
岭表溪洞之民,号为峒僚,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其余不可羁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亦无年甲、姓名,以射生物为事,虫豸能蠕动,皆取食之,谓之山獠。①
可见,“僚”的原意与狩猎有关,许多南方非汉族群僻处山林,一般都具有狩猎技术,并有许多以此为主要生计来源。而华夏民族将这种族群印象特征化、标签化,慢慢地被用来泛指代古代南方非汉族群。因此,如果按生态语境——文化语境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一些族群称谓现象。
三、族群边界冲突与南宋“畲”族群称谓的出现
关丙胜指出:“古代族群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当由自然生态决定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②在本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帝国经略后,给族群格局带来的变化。在福建地区,这种变化在南宋时期变得更为明显,族群的冲突更为严重。
朝廷对一些偏远的非汉人群所在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汀州,一般认为是畲民聚居的地区,在早期也是实行族群自治政策。如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也。”③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畲民的政治管理情况:“被之声教”④说明畲民在礼乐教化,即文化上受到华夏文明的恩泽;“疆以戎索”⑤说明采用羁縻政治,由畲民自我管理。以上两个合起来说明畲族名义上受朝廷管辖,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一种状态。到了宋代,“畲”与汉之间族群开始冲突,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进入汉人的视野中。南宋景定年间,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反映了“畲”汉族群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的情况,刘克庄在《漳州谕畲》开篇写道: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①
由上可知当时族群边界冲突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治中心移到“吴会”(杭州),与浙江相邻的闽西南成为地理版图上“近里”,间接说明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迫近漳州;二是漳州“壤接溪峒”,地理位置上接壤非汉地区,文中又说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所指的“溪峒”应该是潮、梅、汀、赣等地,而宋代盘瓠蛮已广泛分布以上地区,其迁徙呈“向南又折而向东”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显然会遭遇漳州以东强大的汉族势力;三是此时的漳州已呈现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的状态,“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说明“华夷”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突破,族群间互动几率较大,官方出于军事防御考虑也好,出于“严夷夏之防”观念也好,总之漳州的边界冲突已然明显。
漳州汉民与“畲”民族群边界清晰,不仅体现在族称差别上,还体现在刘克庄书中所描述的族群间的巨大文化差异:畲民具有“长技止于机毒”“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猱升鼠伏”的生产生活习俗,“反复杰黠”“自称盘护孙”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的政治待遇。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推论:“畲”、汉两大族群势力此时在一方或彼此扩张过程中,发生边界冲突,在各自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并带有文化偏见,如以“猱”“鼠”的动物习性来形容畲民的习惯等,而恰好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代表刘克庄充当了这历史变化时刻的见证者。换言之,假如话语权掌握在“畲”的手中,其记载定然描述汉人种种负面形象,正如后世流传在畲民中的《高皇歌》所描述的一样。③
漳州“畲”、汉间的族群矛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直到北宋元丰年间,漳州社会比较安定。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风俗形胜时称:“元丰五年(1082年),郭祥正记云:‘闽之八州,漳最在南,民有田以耕,纺苎以为布,弗迫于衣食,乐善远罪,非七州之比也’云云。”①
而过了近200年的南宋刘克庄时代[按《漳州谕畲》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的各族群间的矛盾开始紧张起来:漳州以东为福佬人的势力,潮、梅以西为广府人势力,汀、赣以北则是北方汉人的势力,而闽粤赣交界地区是“溪峒”(有一部分为“畲”)的族群势力。漳州、潮州当时都出现了“畲”“輋”的称呼,宋人蔡襄曾写道:“今来闽中,最急惟是贼盗群众与漳、潮之民为害。”②《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③山斜中的盗贼或“峒獠”应该与“畲”(輋)民有关,乾隆《潮州府志》记载宋宝祐五年(1257年)潮州知州洪天骥防御盐寇、輋民的事迹:
洪天骥,字逸仲,号东岩,晋江人。由朝散郎知潮州,治国事如家事,视民瘼如己疾,治无不为,为无不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历任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公应变设奇,降者相属,又于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为援。且严保伍之令,以澄其源,闻于朝并下之,漳汀仿此。④
可见,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均有不少数量的畲民族群存在。与漳、潮相邻的汀州,在唐宋时期一直被认为是“畲猺”聚居地,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⑤然而“畲”作为一个族群的具体记载却不是首先出现在汀州,而族群边界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其原因。
从唐代以后,王朝在南方广置郡县,在政治上掀起了对福建地区的华夏化运动,中央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边陲,帝国的“开山洞”正是这个运动的表征之一。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南宋偏安,福建与南宋政治中心相邻,这个时期的福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处于历史最发达时期。然而,在福建地区,各地汉族势力发展并不均衡,在开发较早、地理条件较优越的平原、盆地地区如福州、泉州、建州等地,经济文化发达;而开发较晚、地理条件较差的汀州、漳州等地区,仍被认为是“难治”地区,也是“盗贼渊薮”。
古人文人把唐代以前的漳州视为蛮荒之地。柳宗元(子厚)《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刺史》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轻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浸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①
唐朝时期,漳、汀属江南道,封、连则属岭南道。柳宗元谪居柳州“共来百粤文身地”,都是与中原风土截然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的隔绝,更多的是文化的隔阂。再如明人张燮在《清漳风俗考》认为在汉迁徙闽越到江淮以后,漳州是“羁縻瘴乡,声教尚阻”,他继而引用南朝沈怀远的诗句“阴崖猿昼啸,阳亩秔先熟。稚子练葛衣,樵人薛萝屋”,感叹漳州“萧索景象至今可覆案也。”②
唐宋时期的汀州也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汀州的开发时间及进程与均较为滞后,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汀州才被奏置。有的文献将唐宋的汀州视为“穷处”“绝区”,如《舆地纪胜》载:“汀为州,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东接赣水,南邻百粤。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③
《临汀汇考》也将汀州描述是“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④《元一统志》引《广陵志》以诗的形式说明了汀州地理条件的险恶:“全闽形势数临汀,赣岭连疆似井径。江汇重渊锁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⑤
此外,汀州内部蛮夷众多,周围山洞阻隔,北方中原(汉)文化未能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太平寰宇记》称汀州与建州交界的沙县:“自乾符后,土寇乱离,汉路阻隔”。①清代王捷南《闽中沿革表》则称:“……(汀州)其东北境,今长汀、宁化地毗连将乐、邵武一带,自是山洞盘互,道梗未通。”②按此前的理解,山洞应为非汉人群的聚居地,“山洞盘互”则间接说明当时“蛮夷”数量之多。《临汀汇考》则直接说明当时汀州为“峒民”“苗人”散处之地,其文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③
此外,历史上还曾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④之事,该事件足见汀州非汉族群数量之多,汉文化在蛮夷文化中,犹如大海的孤岛。谢重光先生研究发现:南宋时期,虽然汀州城区及附近聚集较大数量人口,但汀州的“外邑”,特别是广大山区呈现出与郡城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经常表现为“一幅基本未开化的蛮夷景象”。⑤其实,闽粤赣地区这种政治中心与周边山区“华、夷”势力状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载:
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⑥
在这种“蛮风蜒雨”中,作为掌握着史料话语权的汉人,把本族群与非汉族群区别开来的方法,就是把族群文化与中原联系起来,如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教授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中写道:“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①这种不断强调“中原文化认同”的叙述模式,反映的是宋代以来,福建本土逐渐融入中原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在表明自身文化历史渊源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其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正统性。②
而同时代的刘克庄描写漳州则称:“风烟绝不类中州”③,谢重光先生将《跋赡学田碑》与刘克庄诗对比后认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区域文化面貌和族群人文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凡此都充分说明,宋代赣南、闽西确已形成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相邻地区迥异的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④唐宋时期漳州与汀州族群格局有所不同。应该来说,汀州的非汉人群比例更高一些,如果以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去探讨不同地区华、夷的族群格局,那么,唐宋时期的汀州,汉人显然是处于孤岛的地位。
实际上,“畲”、汉间的边界是多重的,在族群边界冲突更明显的漳州族群边界更清晰,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族在本族群势力较强的漳州证明他者为“非”(汉),在本族群势力较弱的汀州证明自己为(汉),本质都是在维护族群认同总之,随着南宋时期“畲”、汉边界的划定,“畲”作为一个在文化特征迥异于汉人的特殊族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宋元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中扮演着区分人群的重要的角色。
一、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在唐宋以后,关于南方地区“莫徭”“峒蛮”“蛮僚”的记载日益频繁见诸史料,这既体现华夏族对“他者”认识的加深,同时也是说明南方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一些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上,如谢重光先生指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已经形成了福佬族群。②与中原汉人同时南迁的还有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这些族群“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③,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南方地区汉人与非汉人群的互动,既有族群间的合作,又有族群间的冲突与对抗,唐宋的一些文献记载说明了这点。如《资治通鉴》记载道:“(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甚至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④
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蛮夷”就是畲族先民⑤,滨海蛮夷则应为“蜑民”。这些“洞蛮”以兵和船的形式,为以王潮为代表的汉族势力提供了帮助。再如景福二年(893年),汀州盘瓠蛮酋“钟全慕举籍听命,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潮乃尽有五州之地。”①则说明了一些蛮夷归顺了朝廷,成为中央王朝治理地方的合作者。这种合作间接地说明了南方汉族势力的逐渐增强。
南方汉族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当地汉人对祖居地的解释和建构上《太平寰宇记》在记载“永泰县”时称:“《晋安记》:‘东晋永嘉之乱,渡江衣冠士族多依于此,以求安堵’。当此之时必有县,后人或更改,图未甚详悉。”②
乐史根据《晋安记》的记载,对“晋人衣冠南渡”这一历史事实做出推论,认为当时南迁汉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建立州县,只不过因为建置沿革变迁或记载不详而未能使县名存留于世。这种说法在宋代以后的南方地区颇为流行。“衣冠南渡”成为一种当地汉人祖源历史记忆,并作为文本在福建等地的文献中出现如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代路振的《九国志》称:“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③《八闽通志》卷之三《地理》风俗引《建安志》称建宁府:“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云云。”④
王明珂先生指出,一定的历史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而这种社会情境又与当时的历史心性息息相关。⑤因此我们认为,隋唐以后南方蛮族记载的增多以及汉人祖源地传说的建构,均是在南方地区汉人势力崛起这种社会情境中产生的。
唐宋或更早时期,华南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边缘性不仅反映在政治地理上,更反映在文化阶序上。随着汉族势力在南方地区的增强,处于帝国边缘地区的南迁汉族或当地汉族土著为了提升自己的族群身份,往往对本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上述所举例子说明,当地汉人希望通过回忆或者建构类似“衣冠南渡”的历史来增强华夏认同,从而提升本地汉人的族群地位,并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汉人心目中,早在汉晋时期,本族群的祖先就来到包括福建在内广大南方地区,这进一步证明本地汉人在此地开发、经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汉人增强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两个手段:
一是建构自己的“汉人”身份。如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地方土著积极向汉族或中原王朝靠拢,如积极协助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治机构,“请书版籍”,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后,意味着族群从“化外”向“化内”转变;再者就是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
二是与“蛮夷”划清界限。如在宋代开始,陈元光家族被描述为来自光州固始,且受命于朝廷“平蛮”的中原正统家族。一些非陈姓的汉人,通过建构本族为陈元光“部属”的历史记忆,说明本族与陈元光家族一样,均是中原正统身份。这种历史记忆间接反映了宋明以后,闽南等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通过将本族群与当地蛮夷截然区分,从而建构其本族非蛮的历史逻辑。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献对陈元光记载甚多,陈元光因此被认为是开发漳州的重要人物,以致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开漳圣王,成为流行于闽台诸省重要神明。而实际上,陈元光在唐代的形象与后世的形象相差较大,其中经历了一个历史人物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与闽南地区的汉族认同有特别大关系。唐代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目前所能发现的关于陈元光事迹的文献记载为张鷟的《朝野佥载》,其文称:“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①
作者张鷟的生卒年不详,但生活年代与陈元光相差不远,其所载的关于陈元光内容,纵使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至少反映了时人对陈元光其中一个印象的理解。作者将陈元光这种残暴的性格特征与岭南首领相联系,反映的是北方汉人对南方土著的印象。宋代《太平广记》在引用以上史料时,特意将其置于“酷暴”一节之中。②可以说,唐代时期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且较多为负面形象。从宋代起,漳州地区开始流传陈元光平贼立功的传说,并建庙对其奉祀。宋代漳州令吕璹有诗写道:“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族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③
前文已经说明,宋代时期福建等南方地区汉族意识逐渐增强,塑造陈元光平蛮的形象就是将本族群与“蛮”相区别,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这应该是
陈元光形象塑造的滥觞。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方志、族谱不断塑造陈元光的光辉事迹①,兹不赘述。
由此可见,从唐到宋,及至明清,陈元光的形象逐渐丰满,并以将军、儒士、神明等形象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不断层累、“枝叶其说”的历史建构过程。这种建构的力量来源于闽南等地汉人文化认同的需要。
苏永前通过人类学视野对陈元光“开漳”传说进行分析,他认为该传说的叙事主体为闽南地区中原移民,而传说的产生与传播则是该族群文化认同的主观结果。这种认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圣化”和“神化”,另一方面是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②由此可见,将本族与“蛮夷”区分开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本族群的纯正中原血统身份,这是一种主观认同的表现。
除了陈元光家族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宁化巫罗俊家族。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③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熊修所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④。而巫罗俊的事迹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清代王捷南称:“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①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做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传说本质也同陈元光传说一样,都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②
二、标签化与作为族群文化特征的“畲”
刘志伟通过对清代以后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和民田区研究后发现:二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土地自然形态的差别,实际上是在地方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甚至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记。两个区域之间,除了自然形态的差异外,更存在一种独特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③就此而言,畲田经济与农耕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区别,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阶序、族群格局。确切地说,在华夏民族观念中,从事畲田的族群是不受王化的“非我”族群,而实行农业的则是王朝子民,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华夷之别”。将某一类族群归为“异类”,意味着其无法与华夏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享有同等地位。在唐宋时期,“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充当了“异类称呼”的角色,这种贴标签的过程是伴随着华夏族的族群认知一起进行的。
在隋唐以前,由于南方开发缓慢,作为一种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等词语常用于表示一个地区经济落后、蛮荒化外、教化不及的状态。如《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④《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⑤《汉书·地理志》又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⑥,《盐铁论·通有》云:“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①《晋书·食货志》:“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②《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赎物,以裨国用。”③有的记载甚至直接将“火耕”“水耨”等耕作方式认为是蛮獠的习俗,如《唐大诏令集》载:“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④按照文中意思,“居人”相对于“蛮獠”,应该是汉人;“火耕水耨”是“蛮獠”的风俗,汉人在耕作方式上被同化了。
有的甚至引用春秋以前的休闲耕作制度来形容一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如万历《古田县志》记载如下。
林谞《闽中记》:开元二十八年,都督李亚丘会溪峒逋民刘疆辈千余计归命向化,乃状其事以闻。越明年四月二日,命下允俞而始立邑,当环峰复嶂间,平陆三十五里,版垣墉高丈许,步三百周。树室辟户,张官置吏,子男之邦,周宏远规。先是,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⑤
林谞《闽中记》修于唐大中年间,是福州较早的一部方志,已散佚,林谞事迹见诸《八闽通志》⑥。林谞用“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来解释古田县名的由来,其中“田畯”“敷菑”“疆亩”的典故出自《诗经》《尚书》等文献,⑦均是春秋战国以前休闲耕作制生产及其管理的专用词语。林谞用典的寓意:或者是好古,用典溯及三代,言辞溢美;或者用以说明古田设县之前,该地“溪峒逋民”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可见,主流文化圈时常将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与当地的农业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有一部分记载并不都符合史实,显示的是主流文化圈在“南北问题”上的文化偏见。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与“畬”有关的文学作品,并有许多与山区的非汉民族联系在一起,除了一部分写实、猎奇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畬”来区别族群,如上述所说的莫徭、蛮、獠等。唐宋时期“畬田”农业与一些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的高度重合,原本就带有“华夷有别”文化偏见的汉人将“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类族群身上。
如前所述,唐宋畲田区域逐渐缩小,刚好一些南方山林地带的非汉民族仍保存着这种古代农耕残存形态。如唐代刘禹锡之《莫猺蛮子诗》称莫徭实行刀耕火种,该诗写道: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春。夜渡千仭溪,含沙不能射。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麕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①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一些被称为犵狑、犵獠、犵榄、山猺等非汉族群刀耕火种的习性:“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㺏,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②
畲已然成为非汉族群一种特征,因此也为后来将一部分实施刀耕火种的族群称为“畲”埋下铺垫。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志》中曾对畲民来源进行考证,他说:“考畲民本山越孑遗……畲民山居,亦称山輋或山人……宋谓之畲或輋,以其民居山谷烧田为生,故以此名之。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盖山越也称山民,后人专以山民呼之,寖失越名,以其居于近山之地,遂相呼曰輋。”③饶先生认为,畲民可能源于山越,只不过因为“山居”或“烧田”而被称为“輋”或“畲”,所谓“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言下之意,“輋”和“畲”均为其他族群(主要是汉人)对“山越”的他称。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与畲民有关的诸多称谓,如明清时期“棚民”“菁民”等,这些称谓的出现,与当时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族群标签被贴上后,一些经济方式、经济作物也逐渐与该族群发生联系,这是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如出产于广东、福建等地区的稜(菱)禾,在宋代时并未完全与畲族有联系。《方舆胜览》对梅州程乡的菱禾进行了记载:“土产菱米,不知种之所自出,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粝。”①
而到了明清以后,稜禾(菱禾)均与畲族等非汉民族发生了联系,如明嘉靖《惠安县志》:“畬稻种出獠蛮,必深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②清代《临汀汇考》称稜禾又叫畲米,分为两种,“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两种,四月种九月收,六月八月雨泽和则熟。.”③清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称:“畬稻,种出獠蛮,晋江四十七都多种之。”④再如刀耕火种也打上了族群的烙印,《广东通志》:“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⑤
畲的最初形态除了经济形态,还有与“峒”有相类似的聚落或地名特征。在宋元,畲也被视为地区或聚落的名称,“畲”与“峒”一样,都有一个从“聚落”“地名”到“族群”含义转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转化有时候是可逆的,即:住在“畲洞”里的人被称为“畲民”,而畲民聚居的地方可能又被称为“畲洞”。实际上,南方的许多族群名称都经历了这种转化过程,如瑶,一般认为是由“莫徭”转化而来,因“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⑥再如僚(或獠),按郭璞的《史记·集解》解释为:“僚,猎也。”《索隐》引《尔雅》又云:“霄猎曰僚”。⑦清代梁绍献《南海县志》:
岭表溪洞之民,号为峒僚,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其余不可羁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亦无年甲、姓名,以射生物为事,虫豸能蠕动,皆取食之,谓之山獠。①
可见,“僚”的原意与狩猎有关,许多南方非汉族群僻处山林,一般都具有狩猎技术,并有许多以此为主要生计来源。而华夏民族将这种族群印象特征化、标签化,慢慢地被用来泛指代古代南方非汉族群。因此,如果按生态语境——文化语境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一些族群称谓现象。
三、族群边界冲突与南宋“畲”族群称谓的出现
关丙胜指出:“古代族群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当由自然生态决定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②在本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帝国经略后,给族群格局带来的变化。在福建地区,这种变化在南宋时期变得更为明显,族群的冲突更为严重。
朝廷对一些偏远的非汉人群所在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汀州,一般认为是畲民聚居的地区,在早期也是实行族群自治政策。如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也。”③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畲民的政治管理情况:“被之声教”④说明畲民在礼乐教化,即文化上受到华夏文明的恩泽;“疆以戎索”⑤说明采用羁縻政治,由畲民自我管理。以上两个合起来说明畲族名义上受朝廷管辖,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一种状态。到了宋代,“畲”与汉之间族群开始冲突,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进入汉人的视野中。南宋景定年间,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反映了“畲”汉族群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的情况,刘克庄在《漳州谕畲》开篇写道: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①
由上可知当时族群边界冲突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治中心移到“吴会”(杭州),与浙江相邻的闽西南成为地理版图上“近里”,间接说明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迫近漳州;二是漳州“壤接溪峒”,地理位置上接壤非汉地区,文中又说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所指的“溪峒”应该是潮、梅、汀、赣等地,而宋代盘瓠蛮已广泛分布以上地区,其迁徙呈“向南又折而向东”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显然会遭遇漳州以东强大的汉族势力;三是此时的漳州已呈现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的状态,“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说明“华夷”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突破,族群间互动几率较大,官方出于军事防御考虑也好,出于“严夷夏之防”观念也好,总之漳州的边界冲突已然明显。
漳州汉民与“畲”民族群边界清晰,不仅体现在族称差别上,还体现在刘克庄书中所描述的族群间的巨大文化差异:畲民具有“长技止于机毒”“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猱升鼠伏”的生产生活习俗,“反复杰黠”“自称盘护孙”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的政治待遇。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推论:“畲”、汉两大族群势力此时在一方或彼此扩张过程中,发生边界冲突,在各自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并带有文化偏见,如以“猱”“鼠”的动物习性来形容畲民的习惯等,而恰好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代表刘克庄充当了这历史变化时刻的见证者。换言之,假如话语权掌握在“畲”的手中,其记载定然描述汉人种种负面形象,正如后世流传在畲民中的《高皇歌》所描述的一样。③
漳州“畲”、汉间的族群矛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直到北宋元丰年间,漳州社会比较安定。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风俗形胜时称:“元丰五年(1082年),郭祥正记云:‘闽之八州,漳最在南,民有田以耕,纺苎以为布,弗迫于衣食,乐善远罪,非七州之比也’云云。”①
而过了近200年的南宋刘克庄时代[按《漳州谕畲》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的各族群间的矛盾开始紧张起来:漳州以东为福佬人的势力,潮、梅以西为广府人势力,汀、赣以北则是北方汉人的势力,而闽粤赣交界地区是“溪峒”(有一部分为“畲”)的族群势力。漳州、潮州当时都出现了“畲”“輋”的称呼,宋人蔡襄曾写道:“今来闽中,最急惟是贼盗群众与漳、潮之民为害。”②《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③山斜中的盗贼或“峒獠”应该与“畲”(輋)民有关,乾隆《潮州府志》记载宋宝祐五年(1257年)潮州知州洪天骥防御盐寇、輋民的事迹:
洪天骥,字逸仲,号东岩,晋江人。由朝散郎知潮州,治国事如家事,视民瘼如己疾,治无不为,为无不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历任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公应变设奇,降者相属,又于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为援。且严保伍之令,以澄其源,闻于朝并下之,漳汀仿此。④
可见,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均有不少数量的畲民族群存在。与漳、潮相邻的汀州,在唐宋时期一直被认为是“畲猺”聚居地,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⑤然而“畲”作为一个族群的具体记载却不是首先出现在汀州,而族群边界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其原因。
从唐代以后,王朝在南方广置郡县,在政治上掀起了对福建地区的华夏化运动,中央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边陲,帝国的“开山洞”正是这个运动的表征之一。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南宋偏安,福建与南宋政治中心相邻,这个时期的福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处于历史最发达时期。然而,在福建地区,各地汉族势力发展并不均衡,在开发较早、地理条件较优越的平原、盆地地区如福州、泉州、建州等地,经济文化发达;而开发较晚、地理条件较差的汀州、漳州等地区,仍被认为是“难治”地区,也是“盗贼渊薮”。
古人文人把唐代以前的漳州视为蛮荒之地。柳宗元(子厚)《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刺史》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轻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浸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①
唐朝时期,漳、汀属江南道,封、连则属岭南道。柳宗元谪居柳州“共来百粤文身地”,都是与中原风土截然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的隔绝,更多的是文化的隔阂。再如明人张燮在《清漳风俗考》认为在汉迁徙闽越到江淮以后,漳州是“羁縻瘴乡,声教尚阻”,他继而引用南朝沈怀远的诗句“阴崖猿昼啸,阳亩秔先熟。稚子练葛衣,樵人薛萝屋”,感叹漳州“萧索景象至今可覆案也。”②
唐宋时期的汀州也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汀州的开发时间及进程与均较为滞后,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汀州才被奏置。有的文献将唐宋的汀州视为“穷处”“绝区”,如《舆地纪胜》载:“汀为州,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东接赣水,南邻百粤。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③
《临汀汇考》也将汀州描述是“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④《元一统志》引《广陵志》以诗的形式说明了汀州地理条件的险恶:“全闽形势数临汀,赣岭连疆似井径。江汇重渊锁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⑤
此外,汀州内部蛮夷众多,周围山洞阻隔,北方中原(汉)文化未能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太平寰宇记》称汀州与建州交界的沙县:“自乾符后,土寇乱离,汉路阻隔”。①清代王捷南《闽中沿革表》则称:“……(汀州)其东北境,今长汀、宁化地毗连将乐、邵武一带,自是山洞盘互,道梗未通。”②按此前的理解,山洞应为非汉人群的聚居地,“山洞盘互”则间接说明当时“蛮夷”数量之多。《临汀汇考》则直接说明当时汀州为“峒民”“苗人”散处之地,其文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③
此外,历史上还曾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④之事,该事件足见汀州非汉族群数量之多,汉文化在蛮夷文化中,犹如大海的孤岛。谢重光先生研究发现:南宋时期,虽然汀州城区及附近聚集较大数量人口,但汀州的“外邑”,特别是广大山区呈现出与郡城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经常表现为“一幅基本未开化的蛮夷景象”。⑤其实,闽粤赣地区这种政治中心与周边山区“华、夷”势力状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载:
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⑥
在这种“蛮风蜒雨”中,作为掌握着史料话语权的汉人,把本族群与非汉族群区别开来的方法,就是把族群文化与中原联系起来,如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教授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中写道:“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①这种不断强调“中原文化认同”的叙述模式,反映的是宋代以来,福建本土逐渐融入中原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在表明自身文化历史渊源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其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正统性。②
而同时代的刘克庄描写漳州则称:“风烟绝不类中州”③,谢重光先生将《跋赡学田碑》与刘克庄诗对比后认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区域文化面貌和族群人文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凡此都充分说明,宋代赣南、闽西确已形成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相邻地区迥异的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④唐宋时期漳州与汀州族群格局有所不同。应该来说,汀州的非汉人群比例更高一些,如果以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去探讨不同地区华、夷的族群格局,那么,唐宋时期的汀州,汉人显然是处于孤岛的地位。
实际上,“畲”、汉间的边界是多重的,在族群边界冲突更明显的漳州族群边界更清晰,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族在本族群势力较强的漳州证明他者为“非”(汉),在本族群势力较弱的汀州证明自己为(汉),本质都是在维护族群认同总之,随着南宋时期“畲”、汉边界的划定,“畲”作为一个在文化特征迥异于汉人的特殊族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宋元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中扮演着区分人群的重要的角色。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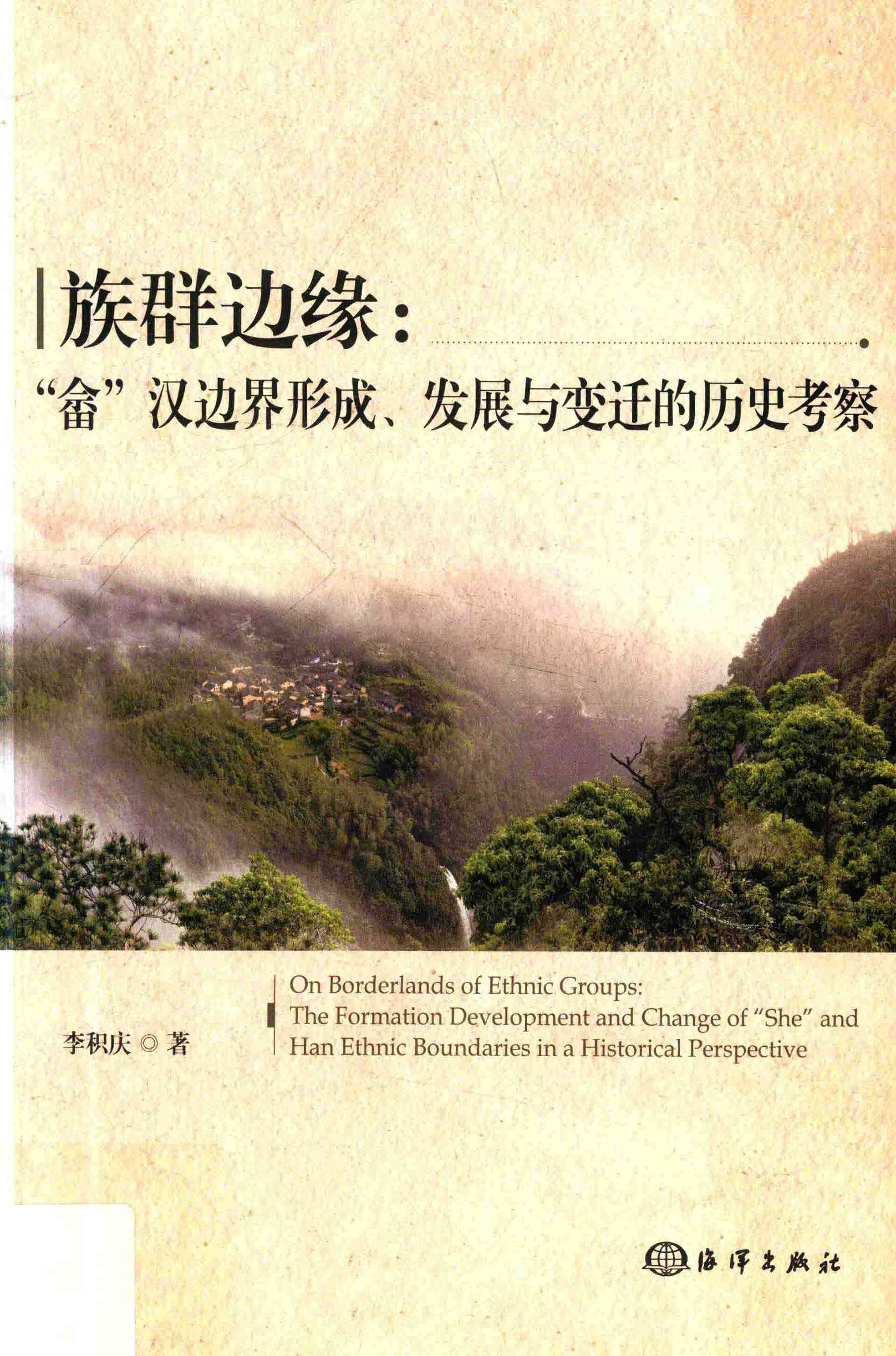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