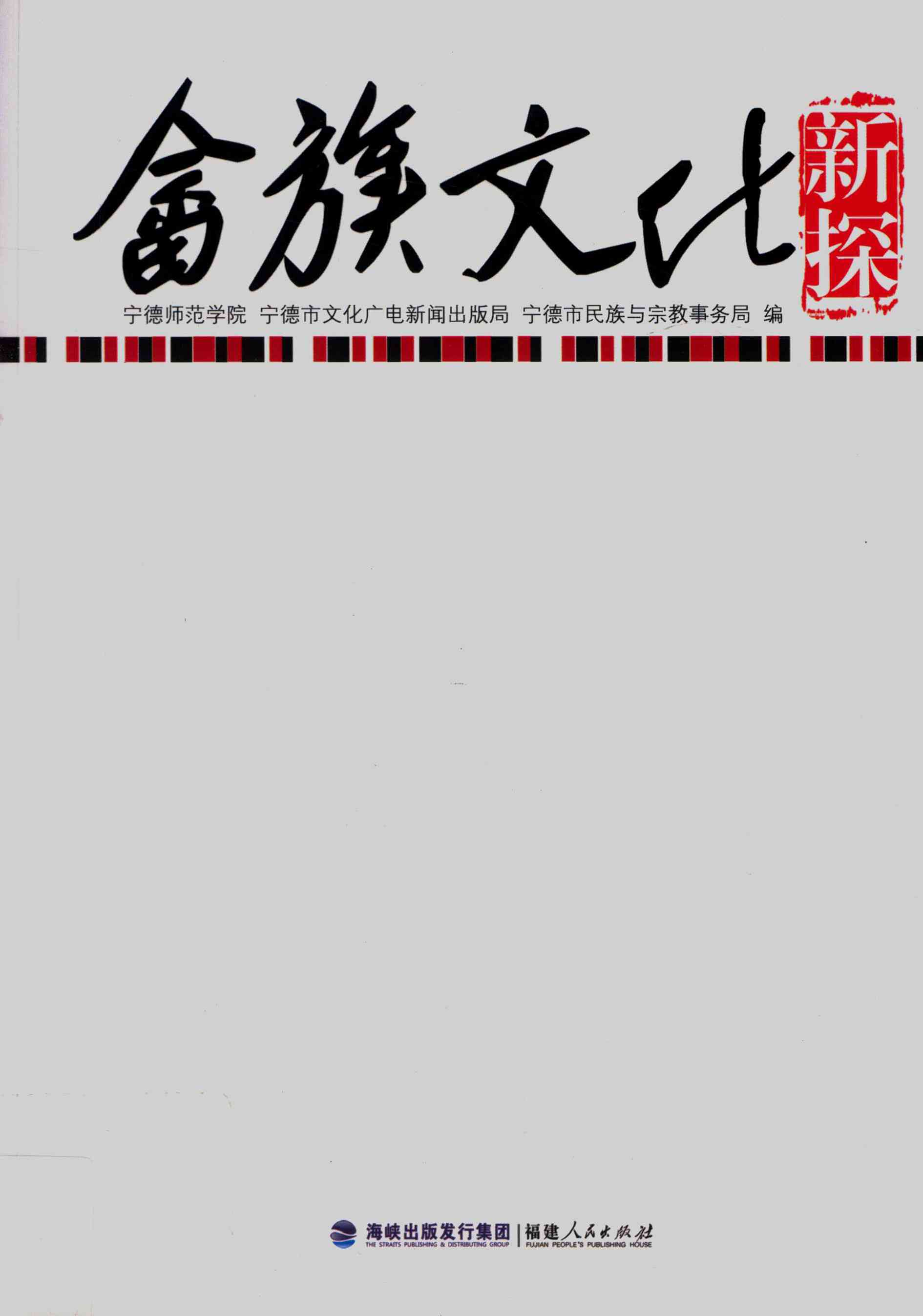内容
根据推算,乾隆中期(18世纪后期)福安县畲民约有1.4万人,在今之闽东范围内当有畲民4万多人。③
人数如此之多的新移民,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散布在闽东的茫茫山野,无疑对这一片土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畲族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使畲族的劳动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周边相同户数的汉族原住民。史料中关于畲族妇女参加劳动的记述可谓比比皆是:“吾族本畲民,男女耕作,自古如斯。”④“畲民……男女杂作,以远近为伍,性多淳朴,短衫跣足。”⑤“畲民……男耕女磕,恪守法纪,其风俗近古。”⑥……
广大畲民定居闽东以后,主动融入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垦荒种山是他们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和周边的汉民一样,他们主要是种植禾稻、蓝靛、苎麻、甘薯等。
南宋以后,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汉人大批南迁,福建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膨胀,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在围海造田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①,“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②是当时的写照。到了明清,闽东大地已经开发得很充分。许多新到的畲民只好到自然条件更为艰苦的高寒山区,开山辟田。这些地方山高水冷,路途遥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畲民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二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农田耕作,极为粗放,水田都只二犁二耙……原始刀耕火种的残余尚留存在耕种之中。1亩水田,种子6斤,插1300株秧苗,故当时就以1300株为1亩。……畲民田园,多为梯田,靠近溪涧能经常灌溉的不多……‘久晴则怕旱,久雨则怕涝’。水利设备极差,无水坝,亦无水渠,顶多只在溪涧水源地方安上竹筒,疏导灌溉,其法十分原始”④。
为解高山梯田水冷、地瘠、耗工、低产之虞,山区农民培植了一种称作山稻或园稻的旱稻。明万历《福安县志》云:福安“又有一种山稻,畲人种于山坞”⑤。这种稻谷适合在山上旱地种植,因多为畲民所种,所以又被称作“畲稻”。畲民“所开土地,叫做‘畲田’……当地群众多称他们为‘畲客’或‘山客’,本无恶意”⑥。
蓝靛也叫青靛,闽东人又叫“菁”。这是一种可以提取蓝色染料的草本植物。明代以来,东南沿海的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对蓝靛的需求激增;“福建菁”已名闻全国,尤以汀州为最,所以有“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之说。因社会生活需要,而且种菁获利颇丰,闽东各县早有种植。万历《福安县志》在《土产》目下就列有“靛”。乾隆《宁德县志》云:“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汀人也”,“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①说明当时有大批汀州人到闽东种菁,其中应该有许多畲民。入迁闽东的畲民,因擅种蓝靛,也被称为“菁客”,他们居住的村落被称为“菁寮”;今福鼎前岐还有一个叫做“菁寮”的畲村。
苎麻纤维细长,平滑而又有丝光,质轻而拉力强,吸湿易干又易散热,染色容易褪色难,历来是闽东山区寻常百姓主要的衣着用料,社会需求量相当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闽东广大的山乡农民无论畲汉,每人至少还有一两件苎麻布制成的被称作“粗衫”的劳动服。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闽东和浙南广袤的山区成了苎麻的理想家园,山民都擅此业。种苎,制苎,直至织成苎布,“一条龙”做到底,自给自足。明末寿宁知县冯梦龙曾有过如此的描述:(寿民)“近得苎麻之利,走龙泉、庆元、云和之境如鹜。……苎山亦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自力其地”②。
种苎与种菁关系甚大,种菁种苎之利数倍于种粮,不少乡民因而致富。清代闽东靛菁除为本地所产苎布着色外,大多销往江浙。此业乾嘉年间(1736—1820年)最盛,同光(1862—1908年)以后,“西洋之靛竞进,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土靛十二斤半仅当彼之十两,色泽较鲜而价较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③。传统的种苎和种靛业遂走向败落。
和汉族山民一样,畲民也擅苎业。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畲民称为“楠机”(nónggū)。“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④苎麻丝织成的布叫做“苎布”、“緕布”、“夏布”。乾隆《福宁府志》称:“夏布之属以福安为上。”①这恐怕与福安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种苎者最多不无关系。
清初,抗清英雄、福安进士刘中藻“选练精兵”,“取于苎寮、菁寮、畲寮”,在“崎岖山谷,聚众万人,遂复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诸县”。②此“三寮”之民的主体应是畲族,收复的庆元等七县都是畲族聚居的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畲民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内容、基本的生活状况。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长乐华侨陈振龙父子从菲律宾引进甘薯(番薯)苗,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大力提倡,开始在福建各地普遍种植。甘薯初一传入便充分表现出耐旱高产的优秀品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山区人民(包括畲民)的主粮。《福安县志》云:“山田硗确,不任菑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粒食,贫民尤利赖焉。”③“薯蓣”即甘薯,“粒食”指米谷。闽东大地山多地少,从此甘薯成为山区人民的主粮,在粮食作物中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畲汉人民不断地对甘薯品种进行改良,以保证持续高产。到民国时期福安就有李薯、蕹菜薯、苦瓜薯、红薯、牛底薯、冰糖薯、台湾薯等品种。④
畲民靠山吃山。除种植业外,采薪烧炭也是畲民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内容和经济来源。20世纪前期的闽东,每50公斤柴片大约可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大约可换10公斤稻谷。畲民常以采薪烧炭换取生活所需。柴薪除松木、杂木片外还有杂木树枝和“细芒”(覆盖山体的芒萁草)。直到20世纪后期“厨房革命”(告别柴草,以液化石油汽或电力为燃料)之前,每天上午在城镇的集市上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山民(主要是畲民)挑着薪炭待沽的身影。
定居的农耕生活使畲民与当地汉族融为一体,并且在保留自己主要传统的同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在政治和文教方面与汉族有了相同的追求。
在耕读文化的氛围中,一些畲族村落也设立私塾,延师授课;一些畲族知识分子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跻身于上流社会;还出现了像古田的富达、霞浦的白露坑等畲族文化名村。封建社会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着畲民,众多畲族宗谱中的“族规”、“家范”都对子孙后代规定了许多充满儒家理念的处世原则,下面这则被称为“圣谕十六条”的教训①颇具代表性: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里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律法以警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戒逃匿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畲族同胞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为闽东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和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以千年的时光,和当地汉族一道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壮丽乐章。
人数如此之多的新移民,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散布在闽东的茫茫山野,无疑对这一片土地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畲族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使畲族的劳动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周边相同户数的汉族原住民。史料中关于畲族妇女参加劳动的记述可谓比比皆是:“吾族本畲民,男女耕作,自古如斯。”④“畲民……男女杂作,以远近为伍,性多淳朴,短衫跣足。”⑤“畲民……男耕女磕,恪守法纪,其风俗近古。”⑥……
广大畲民定居闽东以后,主动融入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垦荒种山是他们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和周边的汉民一样,他们主要是种植禾稻、蓝靛、苎麻、甘薯等。
南宋以后,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汉人大批南迁,福建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膨胀,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在围海造田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①,“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②是当时的写照。到了明清,闽东大地已经开发得很充分。许多新到的畲民只好到自然条件更为艰苦的高寒山区,开山辟田。这些地方山高水冷,路途遥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畲民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二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农田耕作,极为粗放,水田都只二犁二耙……原始刀耕火种的残余尚留存在耕种之中。1亩水田,种子6斤,插1300株秧苗,故当时就以1300株为1亩。……畲民田园,多为梯田,靠近溪涧能经常灌溉的不多……‘久晴则怕旱,久雨则怕涝’。水利设备极差,无水坝,亦无水渠,顶多只在溪涧水源地方安上竹筒,疏导灌溉,其法十分原始”④。
为解高山梯田水冷、地瘠、耗工、低产之虞,山区农民培植了一种称作山稻或园稻的旱稻。明万历《福安县志》云:福安“又有一种山稻,畲人种于山坞”⑤。这种稻谷适合在山上旱地种植,因多为畲民所种,所以又被称作“畲稻”。畲民“所开土地,叫做‘畲田’……当地群众多称他们为‘畲客’或‘山客’,本无恶意”⑥。
蓝靛也叫青靛,闽东人又叫“菁”。这是一种可以提取蓝色染料的草本植物。明代以来,东南沿海的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对蓝靛的需求激增;“福建菁”已名闻全国,尤以汀州为最,所以有“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之说。因社会生活需要,而且种菁获利颇丰,闽东各县早有种植。万历《福安县志》在《土产》目下就列有“靛”。乾隆《宁德县志》云:“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汀人也”,“如西乡几都,菁客盈千”。①说明当时有大批汀州人到闽东种菁,其中应该有许多畲民。入迁闽东的畲民,因擅种蓝靛,也被称为“菁客”,他们居住的村落被称为“菁寮”;今福鼎前岐还有一个叫做“菁寮”的畲村。
苎麻纤维细长,平滑而又有丝光,质轻而拉力强,吸湿易干又易散热,染色容易褪色难,历来是闽东山区寻常百姓主要的衣着用料,社会需求量相当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闽东广大的山乡农民无论畲汉,每人至少还有一两件苎麻布制成的被称作“粗衫”的劳动服。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闽东和浙南广袤的山区成了苎麻的理想家园,山民都擅此业。种苎,制苎,直至织成苎布,“一条龙”做到底,自给自足。明末寿宁知县冯梦龙曾有过如此的描述:(寿民)“近得苎麻之利,走龙泉、庆元、云和之境如鹜。……苎山亦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自力其地”②。
种苎与种菁关系甚大,种菁种苎之利数倍于种粮,不少乡民因而致富。清代闽东靛菁除为本地所产苎布着色外,大多销往江浙。此业乾嘉年间(1736—1820年)最盛,同光(1862—1908年)以后,“西洋之靛竞进,力比土靛强二十倍。土靛十二斤半仅当彼之十两,色泽较鲜而价较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③。传统的种苎和种靛业遂走向败落。
和汉族山民一样,畲民也擅苎业。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畲民称为“楠机”(nónggū)。“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④苎麻丝织成的布叫做“苎布”、“緕布”、“夏布”。乾隆《福宁府志》称:“夏布之属以福安为上。”①这恐怕与福安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种苎者最多不无关系。
清初,抗清英雄、福安进士刘中藻“选练精兵”,“取于苎寮、菁寮、畲寮”,在“崎岖山谷,聚众万人,遂复庆元、泰顺、寿宁、宁德、福安、古田、罗源诸县”。②此“三寮”之民的主体应是畲族,收复的庆元等七县都是畲族聚居的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畲民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内容、基本的生活状况。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长乐华侨陈振龙父子从菲律宾引进甘薯(番薯)苗,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大力提倡,开始在福建各地普遍种植。甘薯初一传入便充分表现出耐旱高产的优秀品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山区人民(包括畲民)的主粮。《福安县志》云:“山田硗确,不任菑畲者,悉种薯蓣以佐粒食,贫民尤利赖焉。”③“薯蓣”即甘薯,“粒食”指米谷。闽东大地山多地少,从此甘薯成为山区人民的主粮,在粮食作物中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畲汉人民不断地对甘薯品种进行改良,以保证持续高产。到民国时期福安就有李薯、蕹菜薯、苦瓜薯、红薯、牛底薯、冰糖薯、台湾薯等品种。④
畲民靠山吃山。除种植业外,采薪烧炭也是畲民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内容和经济来源。20世纪前期的闽东,每50公斤柴片大约可换2.5公斤稻谷,每50公斤木炭大约可换10公斤稻谷。畲民常以采薪烧炭换取生活所需。柴薪除松木、杂木片外还有杂木树枝和“细芒”(覆盖山体的芒萁草)。直到20世纪后期“厨房革命”(告别柴草,以液化石油汽或电力为燃料)之前,每天上午在城镇的集市上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山民(主要是畲民)挑着薪炭待沽的身影。
定居的农耕生活使畲民与当地汉族融为一体,并且在保留自己主要传统的同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在政治和文教方面与汉族有了相同的追求。
在耕读文化的氛围中,一些畲族村落也设立私塾,延师授课;一些畲族知识分子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跻身于上流社会;还出现了像古田的富达、霞浦的白露坑等畲族文化名村。封建社会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着畲民,众多畲族宗谱中的“族规”、“家范”都对子孙后代规定了许多充满儒家理念的处世原则,下面这则被称为“圣谕十六条”的教训①颇具代表性: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里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律法以警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戒逃匿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畲族同胞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为闽东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和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以千年的时光,和当地汉族一道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壮丽乐章。
相关人物
李健民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