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
| 知识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上册》 |
| 唯一号: | 130830020210000318 |
| 人物姓名: | 陈淳 |
| 人物异名: | 字:安卿;号:北溪 |
| 文件路径: | 1308/01/object/PDF/130810020210000002/001 |
| 起始页: | 0227.pdf |
| 出生年: | 1159年 |
| 卒年: | 1223年 |
| 籍贯: | 漳州龙溪(地在今福建省漳州市) |
| 非亲属: | 林宗臣;朱熹;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釆;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 |
传略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地在今福建省漳州市)人,早年在乡村从事童蒙教育活动。师从龙溪林宗臣(字实夫,1133—1189年)。林宗臣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是名儒高登的门人,“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①。据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自述,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他说:
某穷乡晚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蚤闻儒先君子
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已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
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
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
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
《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
《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②
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子至漳州任知州,给久读其书而向往已久的陈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师从机会。然而,一直到十一月在陈淳打消了“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贱氓也。贵贱之分有等”的顾虑之后,在“见贤者之心,油然动于中,终有不容遏”的驱使之下,方以“旧日自警之章为贽”。朱子接到陈淳的求见信,次日就在郡斋接见他,从而使陈淳“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夙愿,成为“今乃得亲睹仪形于州闾之近”的现实。①
《朱子语类》详细记有陈淳初次问学的情形:
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先生
缕缕言曰:“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
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如
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须穷个慈根原来处。仁敬亦然。凡道
理皆从根原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多见士
人有谨守资质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讲论义理,便偏执己见,自立一般
门户,移转不得,又大可虑。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
彻,无有不尽;真见得是如此,决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窥见一班
半点,便以为是。”②
关于穷究根原的教导,对陈淳影响很大。从此,他开始注重义理的辨析,以穷究根原做为上达的工夫。为此,他还撰写了《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等文。朱子对陈淳极为赞赏,“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③。离漳州任后,陈淳还不断地向朱子书信请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中有《答陈安卿》书信六通,书二、书三甚至长达万言。《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有陈淳向朱子请益的“问目”三十六通,内容涉及朱子理学的诸多方面。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一同来到考亭。这是漳州阔别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面向朱子问学。当时,朱子已犯病在床,故朱子每在病床上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自记这一过程说:
十一月中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下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
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
春胡叔器、临川黄毅然二友会。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剧九瘥,每入卧内听
教,而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
学之功而已。①
这便是《宋史·陈淳传》所说的“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②的文献来源。
陈淳前后两次从师虽然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朱子教之“以穷究根原做为上达的工夫”,第二次授其以“下学工夫”,对其思想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在陈淳与其岳父抵达考亭的当天晚上,陈淳又到朱子的卧房内,向朱子表示:“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朱子教导他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③“事事理会”,这是下学的工夫,也是上达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上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朱子对此时“所阙者下学之功”的陈淳一再强调下学之功,就是为了“将来”他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即所谓上达之功。
陈淳对“下学”的理解,最主要的就是致知与力行。“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所谓力行,亦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④这一见解,伴随着陈淳的终身,他在晚年严陵讲学中,将此说写进《用功节目》中,向其后学广泛传播。其中,最能完整而简捷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是《与姚安道》书中所说的:
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格物致知,然后动容周旋无阻。陆学厌繁就简,忽
下趋高,阴窃释氏之旨,阳托圣人之传,最是大病。①
陈淳的两次问学皆有记录,漳州所学名为《郡斋录》,考亭所学称《竹林精舍录》,但原文今均不存。《北溪大全集》中仅有《郡斋录后序》《竹林精舍录后序》两篇序文。《朱子语类姓氏》录其庚戌(1190)、己未(1199)所闻,分别为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庆元五年(1199)在考亭两次从学时所录,其原始文献应即出自《郡斋录》和《竹林精舍录》。
陈淳早年在漳州从事乡村塾师之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故其时他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朱子在其赴考亭二次问学时,劝说“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②。朱子逝世后,为继承和弘扬师说,也为了经历先师所说的“要都经历一过”的游学和讲学实践,陈淳开始了从训童到向成人讲学的变化,在漳州、莆田、仙游等地,以及江浙一带从事讲学,广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严陵讲学。
嘉定十年(1217)五月,陈淳至临安应试,应同出朱门的学友赵师恕(季仁)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同年八月应知严陵府郑之悌等人之邀,于郡庠讲学约两个月。
陈淳的严陵之行,面对的是在“庆元党禁”之后,朱子学备受打击和摧残,两浙的学术空间弥漫着陆九渊的学说,而朱子的学说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严峻现实。陈淳将此描述为“大抵世上一派禅学年来颇旺于江浙间,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堕其中,而严(陵)尤甚”③。“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理气之实。”④为传播朱子学,陈淳在严陵郡庠讲授朱子思想,讲学的内容就是《严陵讲义》。他认为,陆学取消道问学的工夫,“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有严重的阳儒阴释禅学倾向,“不止是窃禅家一二,乃全用禅家意旨,与孔孟殊宗”。①他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不良倾向:
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
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
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②
《严陵讲义》分为《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序》四章,内容是对朱子学的性理体系做提纲挈领的阐述。
在《道学体统》中,陈淳阐述了朱子“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的“一本万殊”的理学思想。他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能之事也,亦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常尔。③
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内在如心,“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外在如身,“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还是对人事而言,“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④这就是朱子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本万殊”思想。
《师友渊源》的主旨是重申道统学说,阐明儒家圣贤之学的递相授受的传承关系。他强调朱子承接儒家道统的重要地位,是在伏羲“首辟浑沦”,周敦颐“再辟浑沦”之后,“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统,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⑤他最后的结论是:
学者欲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当以是为迷途之指南,庶乎有
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准,终不可得其门而入。
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万无是理也。①
在《用功节目》中,陈淳阐述了朱子“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学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陈淳认为“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他说:
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
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
之无不备也。②
在《读书次第》中,他阐述了朱子关于“四书”的进学次序,认为“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需先读,其次是《论语》《孟子》。“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因为“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③
陈淳的严陵讲学,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月的讲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地学者一再挽留,希望他能够继续讲学。陈淳在《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韵》一诗中对严陵之行作了一个小结,也寄托了了他对当地学者的厚望:
道为贤侯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
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
珍重前廊浑气合,督提后进要心通。
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④
陈淳的严陵讲学,与黄榦在临川、汉阳、安庆等地相互应,在朱子逝世后,共同将朱子文化发扬光大,在闽学发展史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朱子是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陈淳继承了朱子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其早年在乡村长期从事童蒙教育活动的实践,也编写了诸多适合儿童阅读的教材,如《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等。
陈淳的重要著作还有《北溪字义》,是陈淳门人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理学入门书。《北溪字义》上下二卷,从“四书”中择取二十六个范畴条目,每拈一字,详论原委始末。以字义研究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深入浅出地诠释朱子学理论的范畴和内涵,是其终身服膺和实践朱子的“事事理会”“下学上达”,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之后,对朱子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此书被视为朱子性理之学的入门书,对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传播海外,特别是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淳晚年频繁的讲学活动,吸引了各地,主要是漳、泉、莆田一带的学者如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釆、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等投身帐下,在闽南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
清人全祖望认为,“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①。四库馆臣评价说:“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平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②
作为朱门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无论是阐发师说或义理,均能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得朱子之真传。清人李清馥评价说:“泉南人文之盛,自紫阳文公倡兴同安,继以白石蔡先生,北溪陈先生宗主文公家法,而士习翕然向风,由是濂洛关闽之书,家弦户诵,号为‘紫阳别宗,”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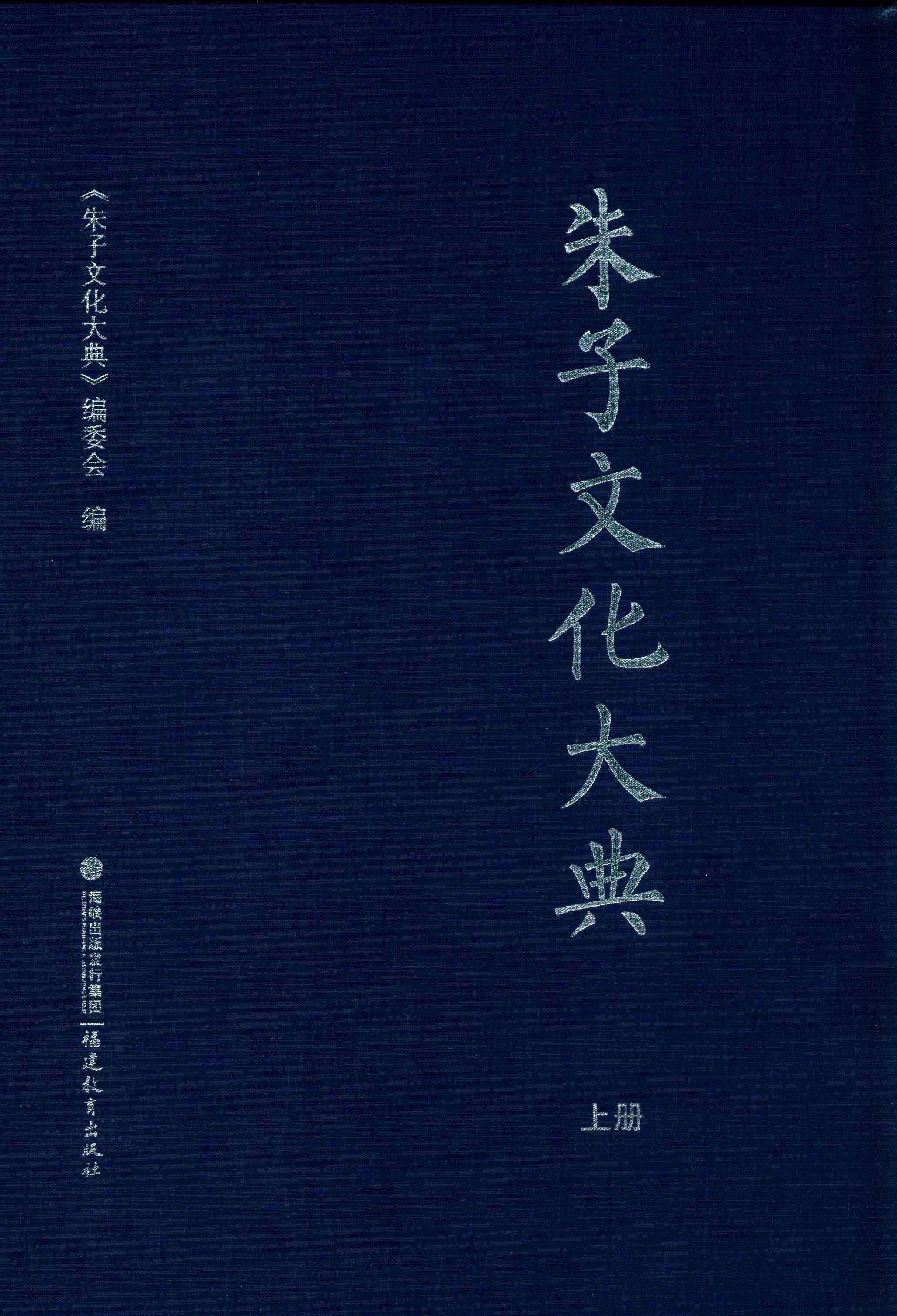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上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朱子文化大典介绍了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 朱子文化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关于构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秩序和普遍价值体系的理论学说。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为构建社会道德秩序和普遍价值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为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和普遍价值体系提供历史根据,这就是儒家的“道统”。二者共同构成了朱子文化的所有内容,涵括了儒家的哲学及其历史文化观。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