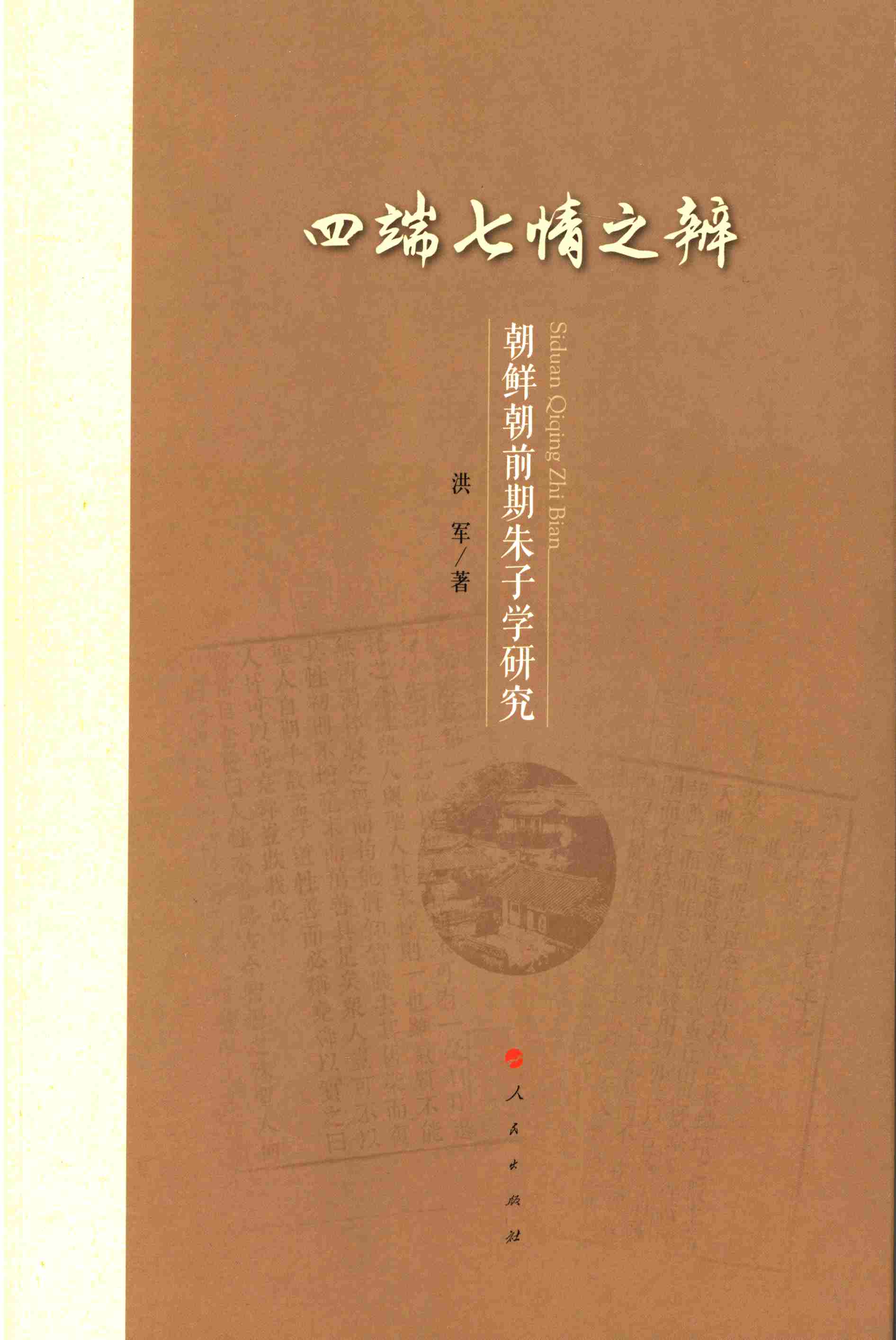二、宋时烈的“四端七情”论
内容
“心”、“性”是理学的核心范畴,因而理学也被称为“心性”之学。性理学之心性学说论域甚广,但首要问题仍是心、性、情、意等概念的定义。从其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中可见性理学之特点。
关于心、性、情、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宋时烈有如下的说明:
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中泻出者也。只言虚灵而不言性情,则是无水之空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虚灵,则是水无盛贮之处也。是三者缺一则终成义理不得,岂得谓之明德乎。盖或者之意,以所谓虚灵不昧者,为释明德之意,故有此说。而不知所谓明德者,是心性情之总名也……盖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意是心之计较也。于一念才动处,便有计较也,心是性情意之主也。此四者虽有性情心意之分说,而只是就那混沦全体上各指其所主而言,其命名殊而意味别耳。不是判然分离,而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是一个地头,意是一个地头也。故心发性发,虽有二名,然心之体谓之性,心之用谓之情,则心性之发,果有二耶。为情为意,虽有分言,然心之才动谓之情,才动而便有计较底谓之意,则情意之用果有分耶?性之发谓之情,虽谓之性发,非无心也;心之发谓之意,虽谓之心发,非无性也……大抵性是无作为底物,心是运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觉闯然出来,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计较谋为底物。①
宋时烈在本段引文中对心、性、情、意之意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重视心的知觉作用,以为“心是知觉运动的物”②,“盖心之为物,洞彻虚灵,天理全具,而又囿于形体之中,则不能无人欲之私矣。”③这说明宋时烈和朱熹一样肯定心之知觉思虑作用。他尤为看重心之虚灵义。“心之虚灵,分明是气欤,先生曰分明是气也。”④从“心是气”到“意”为计较谋为底物——宋时烈所做界说是对李珥“心”论和“意”论的继承。这表明其心性结构亦为心、性、情、意四分之逻辑结构。他也强调“心是气,而性是理。气即阴阳,而理即太极也”⑤。可以看出,在“心”论方面相较朱子,宋时烈更赞同李珥的见解。他继承了李珥“心主心性情意”以及“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的思想。
不过,宋时烈在心论方面特别重视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对此他也以体用范畴进行了说明。“心有真体实用,体如鉴之明,用如能照。”⑥依性理学“体用一源”之思想,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加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中气具有与理一样的超时空之无限性,其心论遂为性理学“天人合一”之范例。宋时烈有言:
道体无穷,而心涵此道,故心体亦无穷。故道谓太极,心为太极。①“心为太极”虽似突兀,但若基于其“理气形三件物事说”亦可推出上述结论。理气统一于形,二者混融无间于心。“大抵心属气,性是理,理气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②
那么,心与性是否是可以合一的呢?在宋时烈看来,“心性虽可谓之一物,然心自是气,性自是理,安得谓之无彼此?”③他进而指出:“所谓性者,虽非舍气独立之物,然圣贤言性者,每于气中拈出理一边而言,今便以气并言者,恐未安。”④
“性”作为与心相对言的范畴成为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概念。朱子把性的意涵规定为仁、义、礼、智。他说:“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⑤,而“性者人之所受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⑥。以仁、义、礼、智为性是朱子学乃至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朱子笃守孟子“性善论”,而力反荀子“性恶论”。因此他总是从性善出发对心、性关系做了论述,“性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⑦。那么“恶”何所从来呢?在此,朱子继承了张载有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以及程颢的“性即气”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⑧。天地之性乃人之本质,气质之性则为人之习染,流衍而为性情才气——前者纯粹至善,后者则有善有恶。二者之关系明显是理与气的关系。
宋时烈是这样理解天地、气质之性的:
所谕天地之性,鄙意有所不然者。盖所谓性者,从心从生,则正以人物已生而言也。于天地下,此性字不得,只可谓之命也。至如张载所谓天地之性云者,亦曰天地畀之性云,非指在天之太极而言也。①他进而指出:
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此二名虽始于程、张,然孔子性相近三字已是兼本然气质而言也。孟子开口便说性善,是皆说本然。然其曰牛之性马之性,则以气质而言也。孟子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及大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此上下文次序似互,然集注所不论则何敢以为然乎。朱子说颇有初晚之异,亦有《语类》、《大全》之不同,不可执一。是此而非彼,徐观义理之所安可也。②
韩国性理学者最为关心的四端七情问题便与此问题密切相关。朱子在论及四端时,曾说过“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这两句话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依朱子的解释,发者是情,而情则属于气,在“理”上不说发。所谓“四端是理之发”,可解释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但是不能说情是从理上发出来的。李滉据此力主“理气互发”,似乎认为理亦能发。其实,依理学之本旨,“理”应为气发时所当遵循的原理,即发之所以然,而实际上的“发者”则是气。
李珥对于朱子的这个思路有相应之契会。他从“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理乘”③以及“理者,气之主宰;气者,理之所乘也”④的思想出发,认为在心所统的性情中未发为性,而已发为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都是性一样,四端、七情也都是情。本然之性不兼气质,气质之性则兼本然之性。同样,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却能兼四端。四端是专言情之善,而七情则兼言情之善恶。“凡情之发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气混融,元不相离。若有离合,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①这就是“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李珥据此解释了情之善恶的问题。他说:“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纯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礼智之端,故目之为四端;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或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理,本于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②本于“气发理乘”之思理,李珥将善恶系于气之清浊。以为“理”无偏正、通塞、清浊、粹驳之异,而所乘之“气”则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清或浊——理既乘于气,便因气禀之善恶亦有善恶。
宋时烈在笃守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前提下,进一步贯彻了“七包四”的思想。
《语类》论大学正心章,问意与情如何。曰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此与先生前后议论,全然不同。盖喜怒哀乐闯然发出者是情,是最初由性而发者,意是于喜怒哀乐发出后因以计较商量者。先生前后论此不翅丁宁,而于此相反如此,必是记者之误也。大抵《语类》如此等处甚多,不可不审问而明辨之也。理气说,退溪与高峰,栗谷与牛溪,反复论辩,不可胜记。退溪所主,只是朱子所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栗谷解之曰“四端纯善而不杂于气,故谓之理之发;七情或杂于不善,故谓之气之发”。然于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岂非纯善乎?大抵《礼记》及子思统言七情,是七情皆出于性者也。性即理也,其出于性也,皆气发理乘之。孟子于七情中摭出纯善者,谓之四端。今乃因朱子说而分四端七情以为理之发气之发,安知朱子之说或出于记者之误也。③七情皆为出于性者,其中发而中节合乎理者即为四端。宋时烈进一步指出:
所谓喜怒哀乐者,不出于性而何?既出于性则谓之人心可乎。序文不曰人心生于形气乎。既曰出于形气,而又以其发于性者当之,岂不自相矛盾乎。如曰四端七情皆出于性,而皆有中节不中节。其中节者,皆是道心之公,而其不中节者皆人心之危也。扩充四端之中节者,则至于保四海,推致七情之中节者,则至于育万物。子思孟子所常接受者,其揆一也。①
七情中中节合理者为四端,即是道心;不中节不合理者皆有人心之危,易流于私欲。宋时烈有言:“盖人心者,非直谓人欲也。其流易入于人欲,若流于人欲,则便为私邪。私之一字,百事之病。故朱子亦尝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此实至言也。”②
宋时烈依其“人心道心”说时提出了“心是活物”的思想。“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者,乃朱子说。如以为可疑,则其所可疑者,乃在于朱子,而不在于栗翁也。大抵吾人亦不深究朱子立言之意,故未免有疑耶。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③“心是活物,其发无穷”——如此说法颇有王学之色彩。宋时烈将其“气”论思想进一步贯彻到心性论领域,其“心”遂较朱子之心更具发用性与活泼性。
由此可见,四端七情问题实质是性情问题。所以顺着“四端七情”之辨自然会引出性情之辨。易言之,性情之辨可视为四七之辨的逻辑延伸。与“两宋”先生同时代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界王夫之(字而农,晚号船山,1619—1692年)则在四端七情问题上提出了“四端非情”论。他认为朱子犯了“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错误。而性情分属天人——如此混淆容易导致“情”对“性”的侵蚀。在船山看来,如尽其性则喜、怒、哀、乐、爱、恶、欲炽然充塞,其害甚大。①船山以为四端不仅是道心,而且还是性。
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为以性为情,知发皆中节之和而不知未发之中也(言中节则有节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节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万殊之理,顺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征性也。有中节者,则有不中节者;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无有不善矣。②
依其之见,应以性情、道心人心来分言四端与七情。从船山与同春的四七见解中可以看到17世纪中韩儒学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向。
总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一致性。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栗谷之学的忠实继承,而且折射出韩国性理学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特点。韩儒往往从“天人一贯”的立场出发,将理气关系之探讨具体落实到人间性理的问题上。四端七情以及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探讨亦犹如此。
关于心、性、情、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宋时烈有如下的说明:
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中泻出者也。只言虚灵而不言性情,则是无水之空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虚灵,则是水无盛贮之处也。是三者缺一则终成义理不得,岂得谓之明德乎。盖或者之意,以所谓虚灵不昧者,为释明德之意,故有此说。而不知所谓明德者,是心性情之总名也……盖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意是心之计较也。于一念才动处,便有计较也,心是性情意之主也。此四者虽有性情心意之分说,而只是就那混沦全体上各指其所主而言,其命名殊而意味别耳。不是判然分离,而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是一个地头,意是一个地头也。故心发性发,虽有二名,然心之体谓之性,心之用谓之情,则心性之发,果有二耶。为情为意,虽有分言,然心之才动谓之情,才动而便有计较底谓之意,则情意之用果有分耶?性之发谓之情,虽谓之性发,非无心也;心之发谓之意,虽谓之心发,非无性也……大抵性是无作为底物,心是运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觉闯然出来,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计较谋为底物。①
宋时烈在本段引文中对心、性、情、意之意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重视心的知觉作用,以为“心是知觉运动的物”②,“盖心之为物,洞彻虚灵,天理全具,而又囿于形体之中,则不能无人欲之私矣。”③这说明宋时烈和朱熹一样肯定心之知觉思虑作用。他尤为看重心之虚灵义。“心之虚灵,分明是气欤,先生曰分明是气也。”④从“心是气”到“意”为计较谋为底物——宋时烈所做界说是对李珥“心”论和“意”论的继承。这表明其心性结构亦为心、性、情、意四分之逻辑结构。他也强调“心是气,而性是理。气即阴阳,而理即太极也”⑤。可以看出,在“心”论方面相较朱子,宋时烈更赞同李珥的见解。他继承了李珥“心主心性情意”以及“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的思想。
不过,宋时烈在心论方面特别重视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对此他也以体用范畴进行了说明。“心有真体实用,体如鉴之明,用如能照。”⑥依性理学“体用一源”之思想,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加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中气具有与理一样的超时空之无限性,其心论遂为性理学“天人合一”之范例。宋时烈有言:
道体无穷,而心涵此道,故心体亦无穷。故道谓太极,心为太极。①“心为太极”虽似突兀,但若基于其“理气形三件物事说”亦可推出上述结论。理气统一于形,二者混融无间于心。“大抵心属气,性是理,理气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②
那么,心与性是否是可以合一的呢?在宋时烈看来,“心性虽可谓之一物,然心自是气,性自是理,安得谓之无彼此?”③他进而指出:“所谓性者,虽非舍气独立之物,然圣贤言性者,每于气中拈出理一边而言,今便以气并言者,恐未安。”④
“性”作为与心相对言的范畴成为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概念。朱子把性的意涵规定为仁、义、礼、智。他说:“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⑤,而“性者人之所受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⑥。以仁、义、礼、智为性是朱子学乃至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朱子笃守孟子“性善论”,而力反荀子“性恶论”。因此他总是从性善出发对心、性关系做了论述,“性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⑦。那么“恶”何所从来呢?在此,朱子继承了张载有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以及程颢的“性即气”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⑧。天地之性乃人之本质,气质之性则为人之习染,流衍而为性情才气——前者纯粹至善,后者则有善有恶。二者之关系明显是理与气的关系。
宋时烈是这样理解天地、气质之性的:
所谕天地之性,鄙意有所不然者。盖所谓性者,从心从生,则正以人物已生而言也。于天地下,此性字不得,只可谓之命也。至如张载所谓天地之性云者,亦曰天地畀之性云,非指在天之太极而言也。①他进而指出:
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此二名虽始于程、张,然孔子性相近三字已是兼本然气质而言也。孟子开口便说性善,是皆说本然。然其曰牛之性马之性,则以气质而言也。孟子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及大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此上下文次序似互,然集注所不论则何敢以为然乎。朱子说颇有初晚之异,亦有《语类》、《大全》之不同,不可执一。是此而非彼,徐观义理之所安可也。②
韩国性理学者最为关心的四端七情问题便与此问题密切相关。朱子在论及四端时,曾说过“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这两句话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依朱子的解释,发者是情,而情则属于气,在“理”上不说发。所谓“四端是理之发”,可解释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但是不能说情是从理上发出来的。李滉据此力主“理气互发”,似乎认为理亦能发。其实,依理学之本旨,“理”应为气发时所当遵循的原理,即发之所以然,而实际上的“发者”则是气。
李珥对于朱子的这个思路有相应之契会。他从“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理乘”③以及“理者,气之主宰;气者,理之所乘也”④的思想出发,认为在心所统的性情中未发为性,而已发为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都是性一样,四端、七情也都是情。本然之性不兼气质,气质之性则兼本然之性。同样,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却能兼四端。四端是专言情之善,而七情则兼言情之善恶。“凡情之发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气混融,元不相离。若有离合,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①这就是“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李珥据此解释了情之善恶的问题。他说:“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纯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礼智之端,故目之为四端;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或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理,本于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②本于“气发理乘”之思理,李珥将善恶系于气之清浊。以为“理”无偏正、通塞、清浊、粹驳之异,而所乘之“气”则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清或浊——理既乘于气,便因气禀之善恶亦有善恶。
宋时烈在笃守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前提下,进一步贯彻了“七包四”的思想。
《语类》论大学正心章,问意与情如何。曰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此与先生前后议论,全然不同。盖喜怒哀乐闯然发出者是情,是最初由性而发者,意是于喜怒哀乐发出后因以计较商量者。先生前后论此不翅丁宁,而于此相反如此,必是记者之误也。大抵《语类》如此等处甚多,不可不审问而明辨之也。理气说,退溪与高峰,栗谷与牛溪,反复论辩,不可胜记。退溪所主,只是朱子所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栗谷解之曰“四端纯善而不杂于气,故谓之理之发;七情或杂于不善,故谓之气之发”。然于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岂非纯善乎?大抵《礼记》及子思统言七情,是七情皆出于性者也。性即理也,其出于性也,皆气发理乘之。孟子于七情中摭出纯善者,谓之四端。今乃因朱子说而分四端七情以为理之发气之发,安知朱子之说或出于记者之误也。③七情皆为出于性者,其中发而中节合乎理者即为四端。宋时烈进一步指出:
所谓喜怒哀乐者,不出于性而何?既出于性则谓之人心可乎。序文不曰人心生于形气乎。既曰出于形气,而又以其发于性者当之,岂不自相矛盾乎。如曰四端七情皆出于性,而皆有中节不中节。其中节者,皆是道心之公,而其不中节者皆人心之危也。扩充四端之中节者,则至于保四海,推致七情之中节者,则至于育万物。子思孟子所常接受者,其揆一也。①
七情中中节合理者为四端,即是道心;不中节不合理者皆有人心之危,易流于私欲。宋时烈有言:“盖人心者,非直谓人欲也。其流易入于人欲,若流于人欲,则便为私邪。私之一字,百事之病。故朱子亦尝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此实至言也。”②
宋时烈依其“人心道心”说时提出了“心是活物”的思想。“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者,乃朱子说。如以为可疑,则其所可疑者,乃在于朱子,而不在于栗翁也。大抵吾人亦不深究朱子立言之意,故未免有疑耶。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③“心是活物,其发无穷”——如此说法颇有王学之色彩。宋时烈将其“气”论思想进一步贯彻到心性论领域,其“心”遂较朱子之心更具发用性与活泼性。
由此可见,四端七情问题实质是性情问题。所以顺着“四端七情”之辨自然会引出性情之辨。易言之,性情之辨可视为四七之辨的逻辑延伸。与“两宋”先生同时代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界王夫之(字而农,晚号船山,1619—1692年)则在四端七情问题上提出了“四端非情”论。他认为朱子犯了“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错误。而性情分属天人——如此混淆容易导致“情”对“性”的侵蚀。在船山看来,如尽其性则喜、怒、哀、乐、爱、恶、欲炽然充塞,其害甚大。①船山以为四端不仅是道心,而且还是性。
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为以性为情,知发皆中节之和而不知未发之中也(言中节则有节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节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万殊之理,顺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征性也。有中节者,则有不中节者;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无有不善矣。②
依其之见,应以性情、道心人心来分言四端与七情。从船山与同春的四七见解中可以看到17世纪中韩儒学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向。
总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一致性。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栗谷之学的忠实继承,而且折射出韩国性理学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特点。韩儒往往从“天人一贯”的立场出发,将理气关系之探讨具体落实到人间性理的问题上。四端七情以及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探讨亦犹如此。
相关人物
宋时烈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