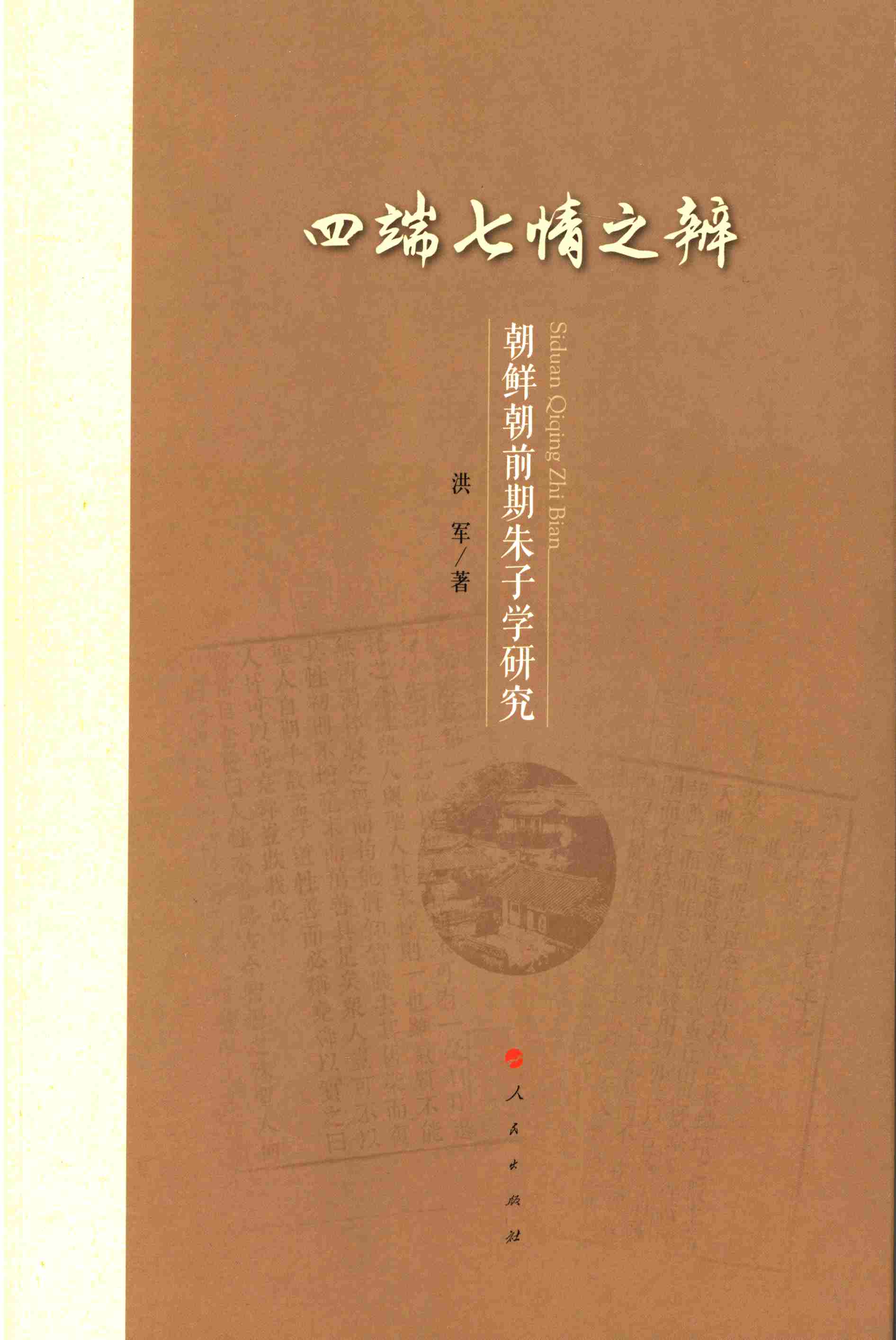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三节 郑道传斥佛论与朱子学“官学”地位之确立
内容
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②)生于庆尚道奉化,是丽末鲜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诗人。他于1362年中进士第,先后在高丽朝任三司右使、右军都总制使等。1392年拥立李成桂(朝鲜太祖,1335—1408年)以创朝鲜王朝,成为李朝的开国功臣。作为性理学者郑氏向往儒家王道政治,提出以宰相制为主的朝政运作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措施,在新朝中央集权的两班官僚体制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朝鲜王朝的设计者”。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而哲学方面代表作有《佛氏杂辨》、《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此外,据传还有《学者指南图》。其中《佛氏杂辨》一书是朝鲜朝排佛崇儒国策的理论根据和基础。
郑道传是丽末重臣、著名朱子学者李穑的门人,同时还是权近的老师。在两朝交替之际,郑氏作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与李成桂相互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抑佛崇儒”的思想文化政策,并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学理上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驳。这是他的主要理论贡献。郑道传在斥佛过程中还吸收程朱的理学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性理学理论。本节仅对其性理学及斥佛论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一、郑道传的性理说
郑道传被称为“东方真儒”。正是通过他的积极阐发和努力,朱子学理气论、心性论的诸多观念和思想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朱子理学亦称为道学,其道器说与理气说密切相连,在新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多数性理学家皆将二说作为思想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借“道”、“器”、“理”、“气”一类的本体论概念探讨天地万物之源也就是世界之本源。
郑道传的道器说大体承袭了程朱的学说。“道则理也,形而上者也。器则物也,形而下者也。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即身心而有身心之道,近而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远而即于天地万物,莫不各有其道焉。人在天地之间,不能一日离物而独立。是以,凡吾所以处事接物者,亦当各尽其道,而不可或有所差谬也。此吾儒之学所以自心而身而人而物,各尽其性而无不通也。盖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者也。”①以形上、形下区分道器的同时,他还强调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性,即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郑道传进而据此批评佛教,指出佛教昧于道器之辨而以道器为二物。“彼佛氏于道,虽无所得,以其用心积力之久,髣髴若有见处。然如管窥天,一向直上去,不能四通八达。其所见必陷于一偏见。其道不杂于器者,则以道与器歧而二之。乃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必欲摆脱群有,落于空寂见。其道不离于器者,则以器为道。乃曰善恶皆心,万法唯识,随顺一切,任用无为,猖狂放恣,无所不为。此程子所谓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者也。然其所谓道者,指心而言,乃反落于形而下者之器而不自如也。”①郑道传主张佛教“道与器歧而二之”的“道器”两极化的思想根于其“万法唯识”、“诸相非相”观念,结果导致“以器为道”,使“道”无别于形而下者之器。这表明郑氏不仅对程朱的道器说有准确的理解,而且对佛教理论要害处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大作《天答》篇中,郑氏弟子权近对其“理”有进一步的解释。“天即理也,人动于气者也。理本无为而气用事,无为者静,故其道迟而常。用事者动,故其应速而变。灾祥之不正,皆气之使然也。是其气数之变,虽能胜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时尔。气有消长,而理则不变,其久而天定,则理必得其常。而气亦随之以正,福善祸淫之理,岂或泯哉。”②以“道则理”和“天即理”来规定“理”,那么“道”和“天”就应理解为“太极”。“无极而太极”——理只是作为万物运动变化之所以然而存,所谓“凡所以为当然之则而不可易者是理也”。郑道传指出理具有无为、不变之特性,气则具有能用事、消长之特性。而且郑氏还把“理”理解为是纯粹而至善的形而上之存有亦即人之性。“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③在理气先后及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了理在气先说以及理主宰气之说,所谓“于穆厥理,在天地先,气由我生,心亦禀焉”④。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四时于是而流行,万物于是而化生。人于其间,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气,以贵于万物而与天地参焉。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又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
在《佛氏杂辨》中,郑道传写道:“盖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太极,而天地万物之理,已浑然具于其中。故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如水之有源,万派流注,如木之有根,枝叶畅茂。此非人智力之所得而为也,亦非人智力之所得而遏也。然此固有难与初学言者,以其众人所易见者而言之。”②理先气后是关乎朱子哲学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理先气后,朱子的思想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年他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是在离开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辨和朱陆太极之辨才逐步形成的。理能生气说曾是其理先气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他的晚年定论则是逻辑在先——此说是在更高形态上返回本体论思想,可谓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对立面的演进和交替,在本质上,是以不同形式确认理对于气的第一位性以及理的绝对性。③郑道传在朱子学这一基本问题上坚持“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的理先气后说。以道器规定理气,以强调二者不离不杂性,从而赋予理以“其尊无对”性——这样的理在气先的理解可以说是郑道传理气说的主要内容。上述思想我们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者的学说中亦可找到其端绪。
儒家以“内圣外王之道”为宗旨:内圣成己,外王成物。而内圣之学实质上也就是心性之学。作为研究人的本质以及自我价值应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内圣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以儒为主),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从而将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因此,理学亦称“道德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说明它是以心性为中心范畴的道德形而上学。
在郑道传的哲学著述中,对心性的论述所占比重较多,如《佛氏杂辨》19篇文章中“佛氏心性之辨”、“佛氏心迹之辨”、“儒佛同异之辨”、“辟异端之辨”以及《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都集中涉及“心性”问题。其中,《心气理篇》的“心”是指佛教的“修心”,“气”是指道家的“养气”,“理”则指性理学的“性理”。即佛教因修心而视现实为虚妄,道家则为养生而否定思虑与分别。而以“理”为生成之理和当为之理的儒家性理学则可兼摄佛道的理论。①
郑道传的心性思想大体继承了朱子的心性情三分构架体系和“心统性情”论。权近在为三峰《心气理篇》中的《心难气》一文加注时说:“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漠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有其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郑道传认为“心”是理气之合,亦为一身神明之舍。此时的心中之理即为所禀之德,所谓“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气之所由生者也”③。他讲到的“德”乃仁义礼智之性,即天之所令而人之所得者。郑氏在《心问》篇中写道:“始者赋命之初,必与人以仁义礼智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为善也。”④人心之理虽为上帝所命,但其义理之公因被物欲所胜,致使其善恶之报也有颠倒。若以义理养心则无物欲之蔽,由是全体虚明而大用不差。郑道传据此提出“志帅气卒”的思想:“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皆不坚守,弃臣从敌,以臣之微,孤立单薄。”⑤权近进一步解释曰:“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亦心之自称也。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注曰,志固心之所之,而气之将帅。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也。心为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徒众而御敌人也。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然志苟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矣。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也”①。“志”是心之所之,心是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众御敌。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志”若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以我一心之微,而当众欲之攻,虽甚微弱而薄劣。因此,郑道传写道:“诚敬为甲胄,义勇为矛戟,奉辞执言,且战且服,顺我者善,背我者恶,贤智者从,愚不肖逆,因败成功,几失后获。”②以为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这便是“内外交相养之道”③。
因“志”为心之所之,故“志”不定则理不能胜私欲,或者说“志”不能统气而制物欲。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若能以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天理,正所谓“方寸之间,私欲净尽,则吾心之理,即在天之理。在天之理,即吾心之理,脗合而无间者也。”④因此,学者“存心养气”应以“以义理为之主”。郑道传指出:“有心无我,利害之趋,有气无我,血肉之躯,蠢然以动,禽兽同归,其与异者,呜呼几希。”⑤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义理也。人而无义理则其所知觉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矣。其所运动者,亦蠢然徒生而已矣。虽曰为人,去禽兽何远哉。此儒者所以存心养气,必以义理为之主也。”⑥将是否存有“义理”视为人异于禽兽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
郑道传的心性论思想在其《佛氏心性之辨》一文中有较集中的论述。他写道:
心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气,虚灵不昧以主于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盖心有知有为,性无知无为。故曰心能尽性,性不能知检其心,又曰心统情性,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则其所具之理,观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彼佛氏以心为性,求其说而不得,乃曰:迷之则心,悟之则性。又曰:心性之异名,犹眼目之殊称至。楞严曰:圆妙明心,明妙圆性,以明与圆分而言之。普照曰:心外无佛,性外无法,又以佛与法分而言之,似略有所见矣。然皆得于想象髣髴之中而无豁然真实之见,其说多为游辞而无一定之论,其情可得矣。吾儒之说,曰尽心知性,此本心以穷理也。佛氏之说,曰观心见性,心即性也,是别以一心见此一心,心安有二乎哉?彼亦自知其说之穷,从而遁之曰:以心观心。如以口齿口,当以不观观之,此何等语欤?且吾儒曰:方寸之间,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其曰虚灵不昧者,心也;具众理者,性也;应万事者,情也。惟其此心具众理,故于事物之来应,之无不各得其当,所以处事物之当否而事物皆听命于我也。此吾儒之学内自身心,外而至于事物,自源徂流,一以通贯,如源头之水,流于万物,无非水也。如持有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物之轻重与权衡之铢两相称,此所谓元不曾间断者也。佛氏曰空寂灵知,随缘不变,无所谓理者具于其中,故于事物之来,滞者欲绝而去之,达者欲随而顺之,其绝而去之者,固己非矣,随而顺之者,亦非也。其言曰,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听其物之自为而已,无复制其是非而有以处之也。是其心如天上之月,其应也如千江之影,月真而影妄,其间未尝连续如持。无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轻重低昂惟物是顺。而我无以进退,称量之也。故曰: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学者所当明辨也。①
可见,郑道传是以程朱心性学说为基础展开了对佛教“性空”论的批评,并得出“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的结论。
二、郑道传的斥佛论
在韩国哲学史上,真正具系统性、理论性的斥佛论的出现始于郑道传、权近师徒。《佛氏杂辨》和《心气理篇》即为反映其斥佛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在同佛教的论战中,郑道传基于儒佛思想之异系统发挥性理学(朱子学)的观点并对佛教根本教义逐一进行了批驳。
《佛氏杂辨》就是一部从性理学的立场出发批驳佛家祈福之虚构性以及僧侣寺庙之弊害的著作。此外,其作还涉及佛教的理论弱点。此书写于1398年,主要围绕以下19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以阐述其斥佛论主张。(1)佛氏轮回之辨;(2)佛氏因果之辨;(3)佛氏心性之辨;(4)佛氏作用是非之辨;(5)佛氏心迹之辨;(6)佛氏昧于道器之辨;(7)佛氏毁弃人伦之辨;(8)佛氏慈悲之辨;(9)佛氏真假之辨;(10)佛氏地狱之辨;(11)佛氏祸福之辨;(12)佛氏乞食之辨;(13)佛氏禅教之辨;(14)儒释同异之辨;(15)佛法入中国;(16)事佛得祸;(17)舍天道而谈佛果;(18)事佛甚谨年代尤促;(19)辟异端之辨。而且,在文中他还援引了许多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人的有关抑佛扬儒的论述。
仅从《佛氏杂辨》题目来看,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是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在驳斥佛教“因果轮回”等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之气化论观点。《佛氏轮回之辨》中提到:
人物之生生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己生者,生而过;未生者,来而续。其间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于是,轮回之说兴焉。《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则知其死也,与气而俱散无复留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天地阴阳之气交合复成人物。到得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复,是变了粗气为物,是合精与气而成物,精魄而气魂也。游魂为变,变则是魂魄相离,游散而变。变非变化之变,既是变则坚者、腐存者込无物也。天地间如烘炉,虽生物皆销铄己尽。安有已散者复合而已生者复来乎?今且验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间,气一出焉,谓之一息。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则人之气息亦生生不穷,而生者过,来者续之,理可见也。外而验之于物,凡草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一气通贯。当春夏时,其气滋至而华叶畅茂;至秋冬,其气收敛而华叶衰落;至明季春夏又复畅茂,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喝饮食煮,煮而尽之;濯衣服者,日曝而干之,泯然无迹。而井中之泉,源源而出,无有穷尽,非已汲之水返其故处而复生也。且百谷之生也,春而种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万,其利倍蓰,是百谷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轮回之说观之,凡有血气者自有定数,来来去去无复增损。然则天地之造物反不如农夫之生利也。且血气之属,不为人类,则为乌兽鱼龟昆虫。其数有定,此蕃则彼必耗矣,此耗则彼必蕃矣。不应一时俱蕃,一时俱耗矣。自今观之,当盛世人类蕃庶,乌兽鱼龟昆虫亦蕃庶;当衰世人物耗损,乌兽鱼龟昆虫亦耗损。是人与物皆为天地之气所生,故气盛则一时蕃庶,气衰则一时耗损,明矣。予愤佛氏轮回之说惑世尤甚。幽而质诸天地之化,明而验诸人物之生,得其说如此,与我同志者幸共鉴焉。
或问子引先儒之说,解《易》之游魂为变曰:魂与魄相离,魂气归于天,体魄降于地,是人死则魂魄各于天地,非佛氏所谓人死精神不灭者耶?曰:古者四时之火,皆取于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热则生火。犹魄中元有魂,魄暖着为魂,故曰钻木出火。又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缘木而存,犹魂魄合而生。火灭则烟气升而归于天,灰尽降而归于地。犹人死则魂气升于天,体魄降于地。火之烟气即人之魂气,火之灰尽即人之体魄。且火气灭矣,烟气灰尽不复合而为火。则人死之后,魂气体魄亦不复合而为物。其理岂不明甚也哉。①“轮回”乃梵文Samāra的意译,原意为“流转”。原是印度婆罗门教教义,后为佛家沿用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宣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得不到“解脱”,则会永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或无阿修罗道而为“五道轮回”)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故称“六道轮回”。这种“轮回”说的核心是灵魂不灭,即人死后其精神不死。根据其人一生所做的“业”,灵魂还会在来生以至二生三生承受业报。①基于灵魂不灭论的“轮回”说是佛教世界观和信仰核心理论。
郑道传以朱子学“气化”论以及“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②。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而“形质”与“神气”必然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人死了精神便无以存在,所谓“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同时,他还提出事物总是处于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中的辩证思想。“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此“生生无穷”之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带有发展进步的质的变化。
郑道传以“气化”和“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说明了人与物类能够不断繁衍的原因,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佛教“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精神不灭论,另一方面也使儒家关于“气”的理论得以挺立和张扬。③他还以此说为基础进一步批评了作为“轮回”之理论依据的“因果报应”说:“或曰吾子辨佛氏轮回之说至矣,子言人物皆得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今夫人则有智愚贤不肖、贫富贵贱寿夭之不同,物则有为人所畜役劳苦至死而不辞者,有未免纲罗钓戈之害、大小强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赋一与何其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释氏所谓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者,不其然乎。且生时所作善恶是之谓因,它日报应是之谓果。此其说不亦有所据欤?曰予于上论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此则轮回之说自辨矣。轮回之说辨,则因果之说不辨而自明矣。”①可见,郑氏是把儒家“气”论思想作为其批评佛教的主要理论工具的。他以朱子学的“气禀”说批驳佛家因缘和合论和因果报应说:“夫所谓阴阳五行者,交运迭行、参差不齐,故其气也有通塞、偏正、清浊、厚薄、高下、长短之异焉。而人物之生,适当其时。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人与物之贵贱于此焉分。又在于人得其清者智且贤,得其浊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贫,高者贵而下者贱,长者寿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虽物亦然。”②
朱熹认为当理化生形气之时,理气浑然相融,具体到形成人物的时候,理即具于形气之中形成人的气禀。人物的气禀不仅有偏与正的问题,还有清与浊的问题。③朱子说过:“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④郑道传援引朱学“气禀”说,进一步指出人与物之区别、人与人之差异皆由气禀的不同造成的,并非出于佛教所谓因果报应。他在《佛氏因果之辨》篇的文末写道:“圣人设教,使学者变化气质,至于圣贤治国者,转衰亡而进治安。此圣人所以回阴阳之气,以致参赞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说,岂能行于其间哉?”⑤可以看出,郑道传反对佛学主要是出于其“灭伦害国性”⑥。因此,他在《辟异端之辩》文中指出:“以予惛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辟异端为己任者,非欲上继六圣一贤之心也。惧世之人惑于其说,而沦胥以陷,人之道至于灭矣。呜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邪说横流,坏人心术,人人得而辟之,不必圣贤。此予之所以望于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⑦
朱熹反对佛学同样出于其对人伦道德的危害性,所谓“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①。不过,其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禅宗。朱熹尝言:“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绝灭犹未至尽,佛则人伦坏;禅则又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故其为害最深。”②此外,他还认为佛教尤其是禅宗将“心”与“性”视为一物,沦空而耽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政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③心性一旦沦空耽寂即如浮光掠影无以致存养之功。由此可见,朱子学与佛学在心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别。④
由上所述,郑道传欲构筑的“善恶因果报应”说既没有借助佛之法力,也没有借助天(上帝)之主宰,而是仰仗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所谓“主体性”。他以为尽管人时有不善之行为,但因“理”的不变性和主宰性,只须力克私欲便可变化气质,从而将不善之行为变为善行。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求人们依靠良善意志和自身努力来战胜“恶”。这说明无论行为之动机还是果报皆系于自身之作为。郑道传的理论虽无佛教因果报应说之效力,却洋溢着合理主义的精神。他确立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大有异于建立在补偿心理之基础上的佛家他律伦理。其说立足人的自律性、自觉性以否定仰赖他力之思想,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⑤可见,郑氏不仅是与李成桂合作成就易姓革命并开创五百年朝鲜王朝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是开启朝鲜朝儒学独尊时代的深远影响的哲学家。
郑道传被誉为“东方真儒”,丽末鲜初排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理学(朱子学)才确立了其在朝鲜朝的官方哲学的地位。而且,通过他的积极阐发,朱子学中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思想皆在此后朝鲜朝儒学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高丽史》有载:“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而正人心,吾东方真一人而已。”①
概言之,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方哲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首先,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被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运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至朝鲜朝初期韩国朱子学已呈现本土化倾向。像李穑的“天则理”思想、郑梦周的春秋大义和心性践履、吉再的节义精神以及基于性理学道器说的郑道传的斥佛论思想等,都为16世纪韩国性理学全盛时期的到来作了理论准备。
郑道传是丽末重臣、著名朱子学者李穑的门人,同时还是权近的老师。在两朝交替之际,郑氏作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与李成桂相互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抑佛崇儒”的思想文化政策,并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从学理上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驳。这是他的主要理论贡献。郑道传在斥佛过程中还吸收程朱的理学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性理学理论。本节仅对其性理学及斥佛论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一、郑道传的性理说
郑道传被称为“东方真儒”。正是通过他的积极阐发和努力,朱子学理气论、心性论的诸多观念和思想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朱子理学亦称为道学,其道器说与理气说密切相连,在新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多数性理学家皆将二说作为思想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借“道”、“器”、“理”、“气”一类的本体论概念探讨天地万物之源也就是世界之本源。
郑道传的道器说大体承袭了程朱的学说。“道则理也,形而上者也。器则物也,形而下者也。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即身心而有身心之道,近而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远而即于天地万物,莫不各有其道焉。人在天地之间,不能一日离物而独立。是以,凡吾所以处事接物者,亦当各尽其道,而不可或有所差谬也。此吾儒之学所以自心而身而人而物,各尽其性而无不通也。盖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者也。”①以形上、形下区分道器的同时,他还强调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性,即道虽不杂于器亦不离于器。郑道传进而据此批评佛教,指出佛教昧于道器之辨而以道器为二物。“彼佛氏于道,虽无所得,以其用心积力之久,髣髴若有见处。然如管窥天,一向直上去,不能四通八达。其所见必陷于一偏见。其道不杂于器者,则以道与器歧而二之。乃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必欲摆脱群有,落于空寂见。其道不离于器者,则以器为道。乃曰善恶皆心,万法唯识,随顺一切,任用无为,猖狂放恣,无所不为。此程子所谓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者也。然其所谓道者,指心而言,乃反落于形而下者之器而不自如也。”①郑道传主张佛教“道与器歧而二之”的“道器”两极化的思想根于其“万法唯识”、“诸相非相”观念,结果导致“以器为道”,使“道”无别于形而下者之器。这表明郑氏不仅对程朱的道器说有准确的理解,而且对佛教理论要害处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大作《天答》篇中,郑氏弟子权近对其“理”有进一步的解释。“天即理也,人动于气者也。理本无为而气用事,无为者静,故其道迟而常。用事者动,故其应速而变。灾祥之不正,皆气之使然也。是其气数之变,虽能胜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时尔。气有消长,而理则不变,其久而天定,则理必得其常。而气亦随之以正,福善祸淫之理,岂或泯哉。”②以“道则理”和“天即理”来规定“理”,那么“道”和“天”就应理解为“太极”。“无极而太极”——理只是作为万物运动变化之所以然而存,所谓“凡所以为当然之则而不可易者是理也”。郑道传指出理具有无为、不变之特性,气则具有能用事、消长之特性。而且郑氏还把“理”理解为是纯粹而至善的形而上之存有亦即人之性。“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③在理气先后及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了理在气先说以及理主宰气之说,所谓“于穆厥理,在天地先,气由我生,心亦禀焉”④。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四时于是而流行,万物于是而化生。人于其间,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气,以贵于万物而与天地参焉。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又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①
在《佛氏杂辨》中,郑道传写道:“盖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太极,而天地万物之理,已浑然具于其中。故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如水之有源,万派流注,如木之有根,枝叶畅茂。此非人智力之所得而为也,亦非人智力之所得而遏也。然此固有难与初学言者,以其众人所易见者而言之。”②理先气后是关乎朱子哲学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理先气后,朱子的思想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年他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是在离开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辨和朱陆太极之辨才逐步形成的。理能生气说曾是其理先气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他的晚年定论则是逻辑在先——此说是在更高形态上返回本体论思想,可谓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对立面的演进和交替,在本质上,是以不同形式确认理对于气的第一位性以及理的绝对性。③郑道传在朱子学这一基本问题上坚持“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的理先气后说。以道器规定理气,以强调二者不离不杂性,从而赋予理以“其尊无对”性——这样的理在气先的理解可以说是郑道传理气说的主要内容。上述思想我们在此后朝鲜朝性理学者的学说中亦可找到其端绪。
儒家以“内圣外王之道”为宗旨:内圣成己,外王成物。而内圣之学实质上也就是心性之学。作为研究人的本质以及自我价值应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内圣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以儒为主),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从而将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因此,理学亦称“道德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说明它是以心性为中心范畴的道德形而上学。
在郑道传的哲学著述中,对心性的论述所占比重较多,如《佛氏杂辨》19篇文章中“佛氏心性之辨”、“佛氏心迹之辨”、“儒佛同异之辨”、“辟异端之辨”以及《心气理篇》、《心问天答》等都集中涉及“心性”问题。其中,《心气理篇》的“心”是指佛教的“修心”,“气”是指道家的“养气”,“理”则指性理学的“性理”。即佛教因修心而视现实为虚妄,道家则为养生而否定思虑与分别。而以“理”为生成之理和当为之理的儒家性理学则可兼摄佛道的理论。①
郑道传的心性思想大体继承了朱子的心性情三分构架体系和“心统性情”论。权近在为三峰《心气理篇》中的《心难气》一文加注时说:“心者,合理与气,以为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愚以为惟虚,故具众理;惟灵,故应万事。非具众理则其虚也漠然空无而已矣。其灵也纷然流注而已矣。虽曰应万事,而是非错乱,岂足为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有其舍,而不知有其主也。”②郑道传认为“心”是理气之合,亦为一身神明之舍。此时的心中之理即为所禀之德,所谓“理者,心之所禀之德而气之所由生者也”③。他讲到的“德”乃仁义礼智之性,即天之所令而人之所得者。郑氏在《心问》篇中写道:“始者赋命之初,必与人以仁义礼智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为善也。”④人心之理虽为上帝所命,但其义理之公因被物欲所胜,致使其善恶之报也有颠倒。若以义理养心则无物欲之蔽,由是全体虚明而大用不差。郑道传据此提出“志帅气卒”的思想:“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皆不坚守,弃臣从敌,以臣之微,孤立单薄。”⑤权近进一步解释曰:“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亦心之自称也。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注曰,志固心之所之,而气之将帅。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也。心为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徒众而御敌人也。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然志苟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矣。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也”①。“志”是心之所之,心是天君。以志统气而制物欲,犹人君之命将帅以率众御敌。故曰“志吾之帅,气吾徒卒”。“志”若不定则物欲得以夺之,而理不能以胜私。故其志之为帅与其气之为徒卒者,皆不能坚守其正,反弃吾心而从物欲。故吾之此心,虽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单弱而薄劣。以我一心之微,而当众欲之攻,虽甚微弱而薄劣。因此,郑道传写道:“诚敬为甲胄,义勇为矛戟,奉辞执言,且战且服,顺我者善,背我者恶,贤智者从,愚不肖逆,因败成功,几失后获。”②以为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这便是“内外交相养之道”③。
因“志”为心之所之,故“志”不定则理不能胜私欲,或者说“志”不能统气而制物欲。若能以诚敬为甲胄而自守,则所以操存者固而志不可夺;若能以义勇为矛戟而自卫,则所以裁制者严而欲不得侵犯天理,正所谓“方寸之间,私欲净尽,则吾心之理,即在天之理。在天之理,即吾心之理,脗合而无间者也。”④因此,学者“存心养气”应以“以义理为之主”。郑道传指出:“有心无我,利害之趋,有气无我,血肉之躯,蠢然以动,禽兽同归,其与异者,呜呼几希。”⑤对此权近则进一步解释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义理也。人而无义理则其所知觉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矣。其所运动者,亦蠢然徒生而已矣。虽曰为人,去禽兽何远哉。此儒者所以存心养气,必以义理为之主也。”⑥将是否存有“义理”视为人异于禽兽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
郑道传的心性论思想在其《佛氏心性之辨》一文中有较集中的论述。他写道:
心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气,虚灵不昧以主于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盖心有知有为,性无知无为。故曰心能尽性,性不能知检其心,又曰心统情性,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则其所具之理,观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彼佛氏以心为性,求其说而不得,乃曰:迷之则心,悟之则性。又曰:心性之异名,犹眼目之殊称至。楞严曰:圆妙明心,明妙圆性,以明与圆分而言之。普照曰:心外无佛,性外无法,又以佛与法分而言之,似略有所见矣。然皆得于想象髣髴之中而无豁然真实之见,其说多为游辞而无一定之论,其情可得矣。吾儒之说,曰尽心知性,此本心以穷理也。佛氏之说,曰观心见性,心即性也,是别以一心见此一心,心安有二乎哉?彼亦自知其说之穷,从而遁之曰:以心观心。如以口齿口,当以不观观之,此何等语欤?且吾儒曰:方寸之间,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其曰虚灵不昧者,心也;具众理者,性也;应万事者,情也。惟其此心具众理,故于事物之来应,之无不各得其当,所以处事物之当否而事物皆听命于我也。此吾儒之学内自身心,外而至于事物,自源徂流,一以通贯,如源头之水,流于万物,无非水也。如持有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物之轻重与权衡之铢两相称,此所谓元不曾间断者也。佛氏曰空寂灵知,随缘不变,无所谓理者具于其中,故于事物之来,滞者欲绝而去之,达者欲随而顺之,其绝而去之者,固己非矣,随而顺之者,亦非也。其言曰,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听其物之自为而已,无复制其是非而有以处之也。是其心如天上之月,其应也如千江之影,月真而影妄,其间未尝连续如持。无星之衡,称量天下之物,其轻重低昂惟物是顺。而我无以进退,称量之也。故曰: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学者所当明辨也。①
可见,郑道传是以程朱心性学说为基础展开了对佛教“性空”论的批评,并得出“佛氏虚,吾儒实。佛氏二,吾儒一;佛氏间断,吾儒连续”的结论。
二、郑道传的斥佛论
在韩国哲学史上,真正具系统性、理论性的斥佛论的出现始于郑道传、权近师徒。《佛氏杂辨》和《心气理篇》即为反映其斥佛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在同佛教的论战中,郑道传基于儒佛思想之异系统发挥性理学(朱子学)的观点并对佛教根本教义逐一进行了批驳。
《佛氏杂辨》就是一部从性理学的立场出发批驳佛家祈福之虚构性以及僧侣寺庙之弊害的著作。此外,其作还涉及佛教的理论弱点。此书写于1398年,主要围绕以下19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以阐述其斥佛论主张。(1)佛氏轮回之辨;(2)佛氏因果之辨;(3)佛氏心性之辨;(4)佛氏作用是非之辨;(5)佛氏心迹之辨;(6)佛氏昧于道器之辨;(7)佛氏毁弃人伦之辨;(8)佛氏慈悲之辨;(9)佛氏真假之辨;(10)佛氏地狱之辨;(11)佛氏祸福之辨;(12)佛氏乞食之辨;(13)佛氏禅教之辨;(14)儒释同异之辨;(15)佛法入中国;(16)事佛得祸;(17)舍天道而谈佛果;(18)事佛甚谨年代尤促;(19)辟异端之辨。而且,在文中他还援引了许多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人的有关抑佛扬儒的论述。
仅从《佛氏杂辨》题目来看,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是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在驳斥佛教“因果轮回”等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之气化论观点。《佛氏轮回之辨》中提到:
人物之生生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己生者,生而过;未生者,来而续。其间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于是,轮回之说兴焉。《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则知其死也,与气而俱散无复留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天地阴阳之气交合复成人物。到得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复,是变了粗气为物,是合精与气而成物,精魄而气魂也。游魂为变,变则是魂魄相离,游散而变。变非变化之变,既是变则坚者、腐存者込无物也。天地间如烘炉,虽生物皆销铄己尽。安有已散者复合而已生者复来乎?今且验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间,气一出焉,谓之一息。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则人之气息亦生生不穷,而生者过,来者续之,理可见也。外而验之于物,凡草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一气通贯。当春夏时,其气滋至而华叶畅茂;至秋冬,其气收敛而华叶衰落;至明季春夏又复畅茂,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喝饮食煮,煮而尽之;濯衣服者,日曝而干之,泯然无迹。而井中之泉,源源而出,无有穷尽,非已汲之水返其故处而复生也。且百谷之生也,春而种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万,其利倍蓰,是百谷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轮回之说观之,凡有血气者自有定数,来来去去无复增损。然则天地之造物反不如农夫之生利也。且血气之属,不为人类,则为乌兽鱼龟昆虫。其数有定,此蕃则彼必耗矣,此耗则彼必蕃矣。不应一时俱蕃,一时俱耗矣。自今观之,当盛世人类蕃庶,乌兽鱼龟昆虫亦蕃庶;当衰世人物耗损,乌兽鱼龟昆虫亦耗损。是人与物皆为天地之气所生,故气盛则一时蕃庶,气衰则一时耗损,明矣。予愤佛氏轮回之说惑世尤甚。幽而质诸天地之化,明而验诸人物之生,得其说如此,与我同志者幸共鉴焉。
或问子引先儒之说,解《易》之游魂为变曰:魂与魄相离,魂气归于天,体魄降于地,是人死则魂魄各于天地,非佛氏所谓人死精神不灭者耶?曰:古者四时之火,皆取于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热则生火。犹魄中元有魂,魄暖着为魂,故曰钻木出火。又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缘木而存,犹魂魄合而生。火灭则烟气升而归于天,灰尽降而归于地。犹人死则魂气升于天,体魄降于地。火之烟气即人之魂气,火之灰尽即人之体魄。且火气灭矣,烟气灰尽不复合而为火。则人死之后,魂气体魄亦不复合而为物。其理岂不明甚也哉。①“轮回”乃梵文Samāra的意译,原意为“流转”。原是印度婆罗门教教义,后为佛家沿用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宣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得不到“解脱”,则会永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或无阿修罗道而为“五道轮回”)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故称“六道轮回”。这种“轮回”说的核心是灵魂不灭,即人死后其精神不死。根据其人一生所做的“业”,灵魂还会在来生以至二生三生承受业报。①基于灵魂不灭论的“轮回”说是佛教世界观和信仰核心理论。
郑道传以朱子学“气化”论以及“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②。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而“形质”与“神气”必然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人死了精神便无以存在,所谓“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同时,他还提出事物总是处于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中的辩证思想。“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此“生生无穷”之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带有发展进步的质的变化。
郑道传以“气化”和“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说明了人与物类能够不断繁衍的原因,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佛教“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精神不灭论,另一方面也使儒家关于“气”的理论得以挺立和张扬。③他还以此说为基础进一步批评了作为“轮回”之理论依据的“因果报应”说:“或曰吾子辨佛氏轮回之说至矣,子言人物皆得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今夫人则有智愚贤不肖、贫富贵贱寿夭之不同,物则有为人所畜役劳苦至死而不辞者,有未免纲罗钓戈之害、大小强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赋一与何其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释氏所谓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者,不其然乎。且生时所作善恶是之谓因,它日报应是之谓果。此其说不亦有所据欤?曰予于上论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此则轮回之说自辨矣。轮回之说辨,则因果之说不辨而自明矣。”①可见,郑氏是把儒家“气”论思想作为其批评佛教的主要理论工具的。他以朱子学的“气禀”说批驳佛家因缘和合论和因果报应说:“夫所谓阴阳五行者,交运迭行、参差不齐,故其气也有通塞、偏正、清浊、厚薄、高下、长短之异焉。而人物之生,适当其时。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人与物之贵贱于此焉分。又在于人得其清者智且贤,得其浊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贫,高者贵而下者贱,长者寿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虽物亦然。”②
朱熹认为当理化生形气之时,理气浑然相融,具体到形成人物的时候,理即具于形气之中形成人的气禀。人物的气禀不仅有偏与正的问题,还有清与浊的问题。③朱子说过:“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④郑道传援引朱学“气禀”说,进一步指出人与物之区别、人与人之差异皆由气禀的不同造成的,并非出于佛教所谓因果报应。他在《佛氏因果之辨》篇的文末写道:“圣人设教,使学者变化气质,至于圣贤治国者,转衰亡而进治安。此圣人所以回阴阳之气,以致参赞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说,岂能行于其间哉?”⑤可以看出,郑道传反对佛学主要是出于其“灭伦害国性”⑥。因此,他在《辟异端之辩》文中指出:“以予惛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辟异端为己任者,非欲上继六圣一贤之心也。惧世之人惑于其说,而沦胥以陷,人之道至于灭矣。呜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邪说横流,坏人心术,人人得而辟之,不必圣贤。此予之所以望于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⑦
朱熹反对佛学同样出于其对人伦道德的危害性,所谓“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①。不过,其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禅宗。朱熹尝言:“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绝灭犹未至尽,佛则人伦坏;禅则又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故其为害最深。”②此外,他还认为佛教尤其是禅宗将“心”与“性”视为一物,沦空而耽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政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③心性一旦沦空耽寂即如浮光掠影无以致存养之功。由此可见,朱子学与佛学在心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别。④
由上所述,郑道传欲构筑的“善恶因果报应”说既没有借助佛之法力,也没有借助天(上帝)之主宰,而是仰仗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所谓“主体性”。他以为尽管人时有不善之行为,但因“理”的不变性和主宰性,只须力克私欲便可变化气质,从而将不善之行为变为善行。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求人们依靠良善意志和自身努力来战胜“恶”。这说明无论行为之动机还是果报皆系于自身之作为。郑道传的理论虽无佛教因果报应说之效力,却洋溢着合理主义的精神。他确立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大有异于建立在补偿心理之基础上的佛家他律伦理。其说立足人的自律性、自觉性以否定仰赖他力之思想,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⑤可见,郑氏不仅是与李成桂合作成就易姓革命并开创五百年朝鲜王朝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是开启朝鲜朝儒学独尊时代的深远影响的哲学家。
郑道传被誉为“东方真儒”,丽末鲜初排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理学(朱子学)才确立了其在朝鲜朝的官方哲学的地位。而且,通过他的积极阐发,朱子学中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思想皆在此后朝鲜朝儒学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高丽史》有载:“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而正人心,吾东方真一人而已。”①
概言之,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方哲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首先,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被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运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至朝鲜朝初期韩国朱子学已呈现本土化倾向。像李穑的“天则理”思想、郑梦周的春秋大义和心性践履、吉再的节义精神以及基于性理学道器说的郑道传的斥佛论思想等,都为16世纪韩国性理学全盛时期的到来作了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