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韩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763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韩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03-220 |
| 摘要: | 这篇文章属于历史研究类文章,主要讲述了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朱子学对朝鲜半岛社会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朝鲜半岛的官方哲学,还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 |
| 关键词: | 朱熹 闽学 研究 |
内容
一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传入朝鲜,经过高丽王朝时期100多年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到14世纪末成为朝鲜李朝的建国理念(即官方哲学),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对此后500余年间朝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期,为朱子学的初传阶段。嘉定十七年(1224)春,朱熹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等到达高丽全罗道的锦城,建立书院讲学,传播朱熹思想,这是朱子学在朝鲜民间传播之滥觞。而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引起统治者重视的则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安垧、白颐正等人。安珦(1243—1306)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朱子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教之正脉,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横经受业者动以百计”。③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④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1298年随忠宣王到元大都燕京,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大量程朱理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珠(颐正)。”①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颇有建树。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
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之所以会在此时传入朝鲜,一方面与高丽同元朝的密切关系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有关。可以说,正是朱子学北传并在元朝取得统治地位,加之高丽同元朝频繁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为朱子学流入高丽疏通了渠道,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程朱理学在中国产生时,汲取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适应了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也为其移植朝鲜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二是14世纪下半期,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阶段。安珦、白颐正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更多地还只是停留在对程朱理学著作的介绍和引进上,还来不及对程朱理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挥,而且传播的规模尚局限于高丽上层极狭小的范围内。进入14世纪下半期,由于朱子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李朝开国后朱子学正式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推动朱子学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
李穑(1328—1396)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李齐贤(1287—1367)是权溥的女婿,曾跟随忠宣王滞留元大都30年,其学注重程朱的“敬以直内”,反对佛教和汉唐经学。李穑年轻时,曾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学者皆仰慕。掌国文翰数十年,屡见称中国”。③官至宰相。他在成均馆任大司成期间,以朱子学为教育内容并对《小学》作谚解,进行普及,任宰相期间,笃力推行儒学教育,在中央建五部学堂,地方设乡校。史载:恭愍王十六年(1367)“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威,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土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月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尘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①后来对朱子学有创见发挥的学者如郑道传、极近等,多出自李穑门下。
郑梦周(1337—1392)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②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③他对朱子学的阐发,同代人颇为折服。“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④李穑曾高度评价郑梦周:“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⑤
郑道传(1337?—1398)号三峰,他不仅是高丽两班改革派的干城,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他“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鸣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邪说,明天理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⑥权近(1352—1409)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受到郑道传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论。权近的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五经浅见录》是继承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李朝时期刊行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溯其发端盖出于权近的《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更是远及日本。
这一时期的高丽朱子学,正是经过李穑、郑梦周、郑道传及权近等的大力推动,加之它适应了当时改朝换代的社会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新王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李朝(1392—1910)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1392年李朝开国。李朝统治者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李朝开国到1876年日本势力入侵朝鲜的近500年间,朱子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甚至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也只有借助朱子学的外衣才能存在。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为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到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退溪学的代表人物李滉(1501—1570),字景浩,号退溪,是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退溪集》(68卷)、《朱子书节要》、《启蒙传疑》、《心经释象》、《天贫图说》、《四端七情论》等。李退溪终身尊信朱熹的思想和学问,武夷山是朱熹晚年弃官隐居和沈潜学问的地方、陶山是李退溪隐居的地方,自古以来又叫作武夷。1183年4月,朱熹54岁时,在武夷山建盖了精舍,翌年写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因物寄兴,沿着武夷山的九曲描写了名胜和景物特色。退溪阅读了《武夷山志》之后,从想象中游览了朱熹隐居的武夷九曲,继承了朱熹《武夷棹歌》的形式,写了《次武夷棹歌》十首,引端了后来韩国各地指称九曲的潮流。如18世纪后期李野淳等人进行的陶山九曲的设定和有关诗歌的创作,他的《陶山九曲》诗次韵朱熹的《武夷棹歌》,又把李退溪的《次武夷棹歌韵》的意向当基础,描写了陶山一带的山水风光。退溪的《武夷棹歌》和韵不仅形成了韩国诗歌史的传统脉络,而且退溪学派的人往往把陶山九曲看成想象武夷和学习朱子的体验空间。①在哲学上,李退溪直宗朱熹,持“理一元论”观点,主张理贵气贱说和理气互发说,重视实践意义的“敬”,强调世界万物产生于“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动静乎”。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先知后行”,强调“性”有纯善无恶的“本然之性”和善恶不定的“气质之性”之区别,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启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之先河。其所创建的陶山书院,至今仍是韩国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书院。退溪学目前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由首尔退溪研究院创办于1973年的《退溪学报》,至今已经发行了一百多期。由退溪学釜山研究院创办的《退溪学论丛》至今也已发行了十余辑。退溪学国际会议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以上。韩国首尔和釜山、日本东京和福冈、中国北京以及香港和台北等城市都曾主办过研讨会。退溪性理学、退溪诗学等相关专题的研究始终都是学界的热点。
这一时期朝鲜朱子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李珥。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世称栗谷先生。1558年去陶山拜李混为师。1564年考中生员、进士科和明经科,历任户曹佐郎、吏曹佐郎、户曹判书、大提学等官职。在因病辞官期间,他回到地方专心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著有《栗谷全书》44卷。李珥反对“理气互发论”,主张“理气兼发论”,创立了朝鲜朱子学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他认为世界是由“气”和“理”所构成,“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理气“浑沦无间”,“实无先后之可言”,同为世界万物之源。但他又认为如论理气先后之分。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官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反对李滉在“性”“情”上的“四七说”,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认为七情以外无四端。李滉、李珥的“四七论争”,开拓了朝鲜朱子学的新领域,后与李滉一起并称为朝鲜思想界的“双璧”“二大儒”。
以李滉为中心的岭南学派(主理派)和以李珥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气派)的论辩持续了长达三百年之久,而这也是朝鲜朱子学的成熟期和巅峰期。到了16世纪末,朱子学逐渐从学术论辩转到与理论研究无关的“礼论”等问题,甚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党争工具。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畿湖学派分化为“老论”和“少论”。“老论”学者将朱子学化为绝对理念,并以自己的理论为朱子学正统。“少论”学者则反对朱子学绝对化甚至批判朱子学,还出现了郑齐斗(霞谷,1649—1736)这样的朝鲜阳明学大家。与此同时,岭南学派中则出现了“实学”之风,从“利用厚生”的观点来批判观念化的朱子学,谋求儒学的新方向。如以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的“实事求是学派”,主张在研究经典时依确实的考证,理解文本真正的意义;以李翼(星湖,1681—1763)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关心土地制度和行政改革)和以朴趾源(1737—1805)为中心的“北学派”(振兴农业、主张工商业的流通和生产技术革新)则主张理论研究要对现实社会的文物制度和社会文化政策有贡献。实学派观点的集大成者是丁若镛(茶山,1762—1836)。他主张土地和社会制度改革,重视科技,这既使朝鲜从性理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也间接加速了朱子学在朝鲜的衰落。
二 当代韩国的朱子学的研究
(一)20世纪初的朝鲜朱子学。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面对西学的渗入,朝鲜朱子学内部分化为传统论派、开化论派和调和派。三派的思想特点及其研究方法大致如下。
传统论派开展卫正斥邪运动,有原教旨主义的特点,大都奉行尊华攘夷的义理思想,秉持朱子“理尊气卑”的形上学,视儒学为理、为王道,西学为气、为霸权主义。按照朝鲜朱子学思想体系的两大派——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①——来划分,岭南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震相(号寒州,1818—1885)、张福枢(1815—1900),畿湖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柳麟锡、田愚(号艮斎,1841—1922)、朴世和(1834—1910)等②。由于我们的关注点是当代朱子学,这里将略去对几位19世纪的传统论者思想的考察,而关注柳麟锡、田愚这两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论者的思想。
柳麟锡主张,儒者在国家变乱之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态度:第一,发起义兵以扫清逆党;第二,即使离开国土,也要守住旧制度;第三,奉献生命以遂成其志。③他的理论依据是理尊气卑、理主气客的思想。他指出,“其所本者理,所形者气,而理气元是帅役上下”①。但他的兴趣点并不在讨论理气的关系,而在于以此为依据,强调民族自主和确立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批判当时朝鲜的西化倾向。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五伦”乃是据于天理,而西方的新教育则只是追求形气以满足欲望,因此是应当拒斥的。另外,西方新教育的推行是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之一,所谓的西化不过是日本希望引导朝鲜脱离清室、逐步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实现韩日合并的奸邪诱饵。
类似地,田愚的研究也是将性理学作为理论基础,而着眼于解决当时韩末的社会危机。不过,他的性理学主张与柳麟锡的有冲突。在《两家心性尊卑说》(1918)一书中,田愚指出了他的性理学主张与其他学派的主张的不同:他主张“性理心气论”,认为心是气而不是理,因为心并非静而无为,而是动而有为的;相比之下,其他学派则主张心主理,而没有看到心须依理合理才能无偏失的道理。在此基础上,田愚在《从重时中辨》(1905)一文中指出,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体现“性即理”说,而夷狄和异端则只能随“心即气”的欲望思考和行为②。与此相呼应,田愚在《与郑君祚》(1877)③、《论裴说书示诸君》(1908)④等一系列书信中提出,应对当时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当权者作性理学的内圣修养,并施行排斥夷狄之开化论的政策。随着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加剧,田愚选择了隐遁守旧而力保华脉,将余生奉献给了朱子学乃至中华文化的教育和写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论派主要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即他们对朱子思想和著作的讨论是以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为旨归的。
再来看开化论派。秉持开化论的学者们⑤积极接受西方新学(主要是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进化论),批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的无用性,提倡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甚至将被日本殖民的亡国原因归咎于儒学,以为朱子学空谈心性,阻碍智力发展,并以腐朽思想求生存,实乃缘木求鱼①。
最后来看调和派。调和派由一些活跃于政界的儒者组成,提倡以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体新用论或儒体西用论,反驳开化论对儒学的批判,认为开化不是无条件地仿效西方,而是要适合自己社会的现况。这一派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如朴殷植、金允植,等等)是韩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②。调和派鲜有朱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是持批判朱子学的立场的。其中,朴殷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朴殷植在早年(1859—1897)属于传统论派,仅以朱子学为正学。在经历了甲申政变(1884)、清日战争、甲午更张(1894)等事件之后,朴殷植看到了传统论派在对抗日本侵略上的无力性,遂转而批判朱子学。他一方面创立“大同教”(1909),作为儒家改革的主体;另一方面,推广阳明学,批判朱子学。在《儒教求新论》(1909)一文中,朴殷植指出了朱子学的三大弊病:第一,朱子学只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工具,与儒家的根本政治思想(民本主义和大同主义)相背离;第二,朱子学只是消极布教的权威主义而已,偏离了孔子周游列国思以易天下的理念;第三,就学问本身来说,朱子学支离繁杂,所讲的“知”与新学的科学之知是同一知识层次;而阳明学的良知则高于科学知识,可以吸收各种科学,纳于良知之学内。③类似于传统论派,朴殷植也同样运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只是他的通经致用方法是从批判朱子学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朱子思想,比如,将朱子学在现实运用中的教条化归咎于朱子思想本身,并将朱子的“知”等同于闻见之知。
(二)1905—1945年的朝鲜朱子学。
1905—1945年期间,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朱子学作为朝鲜本国文化传统的代表而遭到了歪曲①甚至废止,这令20世纪初传统论派的复兴朱子学努力严重受挫。朱子学乃至儒家文化都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处于低谷期。尽管如此,一些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却仍致力于延续朱子学和儒学的命脉。这段时期内比较著名的朱子学和儒学成果有: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何谦镇的《朱子書節要》(1939)、《东儒学案》(1943)。
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是韩国首部近代儒教通史。张志渊曾任《时事丛报》《皇城新闻》的主笔,并在满洲条约签定时,发表社论《是日也放声大哭》(1905),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在《朝鲜儒教渊源》一书中,他受到韩国实学的影响,将奉行朱子学抽象理论的性理学家斥为小人儒,与他所推崇的李翼(星湖)、丁若镛(茶山)等君子儒区分开来,认为朝鲜李朝衰亡原因是因未用君子儒或真儒。他既批评传统论派不知变通、拘泥于性理和训诂,又批评开化论派不懂得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盲从西学之浅表,认为二者均失其中,主张儒教伦理与近代科学可以参互变通。他表示,西方的科技是近三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故论古代文明,则东方优于西方,只是旧儒们拘泥固执,而使儒学浮虚无灵,才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衰落。
何谦镇(1870—1946)堪称以道统为己任的典范。他本人曾以儒者身份参与独立运动,并两次入狱,并于1931年创立“德谷学堂”,晚年著书立说,致力培养后学。他的《东儒学案》(1943)可以算作朝鲜儒学史上唯一的学案。朝鲜儒学史上类似的著作是朴世采的《东儒师友录》(1682)和宋秉瑄的《浿东渊源录》(1882),但在影响力上皆不及《东儒学案》。《东儒师友录》包括了薛聪以下的750位学者,但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他们的师友渊源和行迹的,而不是关于思想。另外,这些被选择的人物大都是畿湖学派的学者,时代也局限于18世纪后期。《浿东渊源录》参照了朱子《伊洛渊源录》的体例,兼参《东儒师友录》,主要记述人物的思想渊源,多引用关于人物行迹的材料,而不是人物的思想观点,且未区分学派。相比之下,《东儒学案》则要全面很多。《东儒学案》分为上、中、下三册二十三篇,每个学案里,都包括学派来源、代表学者的生平和学问特性、思想特色等内容。何谦镇以道统论的观点成书,认为理学为儒学正统,并以朱子学为理学正统,以退溪学派为中心。尽管本书重视道学义理实践、而不注重性理学的哲学理论和各学派的学问异同,从而未论及朝鲜阳明学派(江华学派),但是全书对各个理学学派的分殊和脉络均有细致而公允的分析和评价,这使得此书的分类构图一直为人所称道,也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不失为研究韩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一项重要参考文献。
(三)20世纪40—70年代初的朝鲜朱子学。
1945年之后,朱子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处于低谷期。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在经历了促进韩国近代化进程的甲午更张运动以及日本实行的彻底抹杀韩国传统文化的政策之后,中断的文化传统已很难迅速复苏。第二,光复之后的韩国处于文化过渡期,而朱子学没能通过自我改革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力与其他各类文化竞争,当然也不能主导韩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三,美国军政时期(1945—1948),西方文化渗入,致使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很难一枝独秀,韩国民众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很难对朱子学有亲近感,加之韩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逐渐西化,仅有极少数韩国大学维持朱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命脉。第四,韩国政府和民众都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富裕上,进一步造成了传统伦理价值的危机。第五,在经历朝鲜李朝崩坏、日本殖民统治之后,20世纪的韩国基本上每十年有一动荡,50年代南北对峙、60年代学生民主革命和军事政变、70年代实施巩固维新独裁体制,韩国社会处于长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中,这对于20世纪初就岌岌可危的韩国朱子学来说,无疑又是新的挑战。特别是50年代的南北对峙以及60年代实学思想的复兴(克服朝鲜朱子学空谈心性的倾向,力求回到原始儒学的质朴面貌,兴起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都是对朱子学研究的阻碍。
1945年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论著有:玄相允《朝鲜儒教史》(1949);李丙焘《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1959)以及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郑寅普、李相殷的著作。
玄相允的《朝鲜儒教史》采用文本考据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朝鲜朱子学两大富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对峙为主线,勾画出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脉络。李丙焘的《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则采用了史学研究方法,考察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朝鲜的发展轨迹,着重于梳理这两派在朝鲜的历史流变,而不是进行思想分析和论述。
郑寅普和李相殷的著作可以被看作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两大思想体系——阳明学现代新儒学和朱子学现代新儒学——之间的争论的绝佳范本。同为韩国现代新儒家,两大思想体系皆主张兼采东西学术之长,综合新旧之学,但对何为东方学术之长的问题有争议。郑寅普著有《阳明学演论》①,继承了20世纪初的朝鲜阳明学家朴殷植的批朱立场,认为阳明学与朝鲜民族意识能自然结合,圣贤之道在于人心未亡,而其人情自身则是至善良知的表现;而朝鲜儒学流弊则生于朱子学,朱子学或讲论心性而少于己身的良心契合,或标榜道义却以此图谋私利②。李相殷则是朱子学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他著有《〈大学〉〈中庸〉之现代的意义》《再论东洋文化》《从humanism看儒教思想》《批判国史教科书之性理学叙述》《儒学与韩国思想》③《四七论辩及对说、因说的意义》④等,旨在匡正对朱子学的流俗偏见,并试图熔铸朱子学与现代学问。类似郑寅普,他也提倡修正儒学重义轻利、内本外末的思想,主张兼顾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但他认为朱子学的性理之学并不像阳明学者理解的那样与现实生活相疏远,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的,从而实学并不与性理之学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无实学之性理学为空虚,无性理学之实学为盲目也。”⑤具体说来,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当今价值在于三方面,其一,看到制度的制定和改革并非万能,制度操作者的道德性更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教义是基础;其二,西方的历史呈现出对立分裂形态,而儒家则提示出一条合作、统一之道,比如,秦、汉统一就与儒家的政治哲学经典《大学》和心性哲学经典《中庸》的出现关系密切;其三,肯定朱子对《大学》的格物释义,认为其具有科学精神,可以视为清代实学和韩国实学的鼻祖,朱子学较之陆王学,具有更踏实的学风和现代意义。
(四)多元化时期的朝鲜朱子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韩国社会的国际化,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开始流行,其中不乏正视传统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在各个大学重视复兴传统文化、增加研究人员以深化学术研究的风潮推动下,为朱子学的复兴带来了新的生机。韩国学界甚至兴起了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并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韩国学者梁承武(2008)的统计,从80年代开始,有关朱子学方面的单行本、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等各类论著较80年代前有了极大增长,而研究广度也极大提升①。就广度来说,这些研究涉及了朱子及朝鲜历代朱子学大家的哲学思想(以理气论、工夫论等方面的研究业绩较为丰厚)、散文和诗歌研究、教育思想,等等。然而,从研究的深度来说,70年代之后的朱子学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大多数研究都缺乏思想上的创新意识,而以客观、逻辑性的思想史研究或文本研究为基本特征,即只停留在研究朱子和历代朱子学大家的思想、论著和言行的层面,把儒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从70年代至今,涉及韩国朱子学史研究的论著及论文主要有:裴宗镐《韩国儒学史》(1974)②、《韩国儒学资料集成》(1980),李东俊《关于17世纪韩国性理学派历史认识的研究》(1975)③,韩永愚《朝鲜前期性理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1976)④,柳承国《韩国的儒教》(1976)、《东洋哲学研究》(1983)⑤、《韩国儒学史》(1989)⑥,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1980)⑦、The Korean Controversy over ChuHsi's ViewontheNatureofMan and Things(《韩国学界关于朱熹论人、物之性的争论》,1982)①、《东洋思想与韩国思想》(1984)②、《退溪李滉的哲学思想》(2000)③,权延雄《世宗朝的经筵和儒学》(1982)④,李楠永《理气四七论辩与人物性同异论》(1984)⑤,琴章泰、高广稷《儒学近百年》(1984)⑥,金忠烈《高丽儒学史》(1984)⑦、《韩国儒学史》(1998),李成茂《朱子学对十四、十五世纪韩国教育及科举制度的影响》(1986)⑧,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 (1986)⑨、 《韩國儒学史》 (1987),玄相允《韩国儒学史》(1986)⑩,崔英辰的五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史》(1997),姜在彦《韩国儒学两千年》(2003),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室编的七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大系》(2005—2007),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2008)⑪,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2011)⑫,等等。其中也不乏研究韩国大儒的思想的论著,如韩永愚《郑道传思想研究》(1983)⑬,李东翰《技术之危机与敬哲学之解答》 (1988),申龟铉《西山真德秀之〈心经〉与退溪李滉之心学》(1988),李基东《李退溪的人道主义和敬》(1988),丁淳睦的《朱晦庵和李退溪之书院教育论》(1988)⑭。还有一些是比较韩国儒学与其他国家儒学研究状况的论著,如,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1995)①。
这些论著主要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梳理朱子学在朝鲜的发展脉络(或某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或者横向考量朝鲜朱子学研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朱子学研究之间的异同。比如,裴宗镐(1974)探讨了朝鲜性理学的主要议题——四端与七情论辩及理气论争——的演变过程及论争的焦点所在;柳承国(1976,1989)探讨了朱子学传入高丽的经过以及朝鲜性理学的兴盛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尹丝淳(1980,1984)则以对韩国儒学的特性为分析主线,探讨了韩国神话传说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的权威地位的关系(他认为,韩国神话传说揭露出韩国文化对于超越问题的兴趣,使得性理学家对于朱子学中的“天命”“天人合一”“穷理”等问题有细致的、突破性的讨论)、朝鲜前期和后期思想家对于“实学”和“虚学”的看法的不同(朝鲜前期儒者以佛学为虚学、性理学为实学,后期实学派则以超越训诂和辞章、袖手谈心性的性理学为虚学,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之学为实学),等等。有时,这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以客观叙述为旨归的,而是带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这种研究带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论预设,比如,金忠烈(1984,1998)的儒学史叙述是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儒学并非宗教,不认同来世,而是追求现世的现实主义;而琴章泰(2011)则主张,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并从朝鲜历史上积极实践儒学价值的儒学家的具体功绩研究入手(比如张志渊、何谦镇等儒者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奔走、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等),研究儒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第二,这种研究方法是与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比如,李东翰(1988)、申龟铉(1988)、李基东(1988)、丁淳睦(1988)都是试图通过将研究退溪思想与探讨其现代意义结合起来,为现代社会确立价值目标。不过,从总的研究倾向上来看,大部分采用史学研究方法的论著还是从客观的角度切入的。
除了对韩国朱子学史的研究,70年代之后的韩国朱子学研究也涉及对朱子本人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训诂考据的方法;二是义理研究的方法;三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了训诂考据方法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朱子论著的韩文注译工作。根据梁承武(2008)的考察①,在韩国出版发行的朱子学译著主要有《四书集注》、《小学集注》、《诗集注》②、《朱子家礼》③、《朱子家训》④、《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到卷六“性理三”部分⑤、《近思录》⑥,等等。至今,尚无朱子全套著作的完整韩注本问世,甚至一些朱子的重要著作(如,《四书或问》《仁说》,等等)亦未有韩注本。
运用了义理研究方法的朱子学研究代表作是金永植(Yung SikKim)的一系列朱子学著作。由于他的研究以往较少被讨论到的朱子自然哲学为关注点,发前人之所未发,笔者拟用一定篇幅介绍他的研究内容。
金永植在2000年出版了专著TheNatural Philosophy ofChiHsi(1130—1200)(《朱熹的自然哲学1130—1200》)⑦,研究朱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将朱子的自然哲学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相比较。他首先讨论了朱子自然哲学中的基本概念——理、气、阴阳、五行、象数,等等,并兼论鬼神、天和圣人这些虽“不属于自然世界、但仍与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有关”⑧的事物。接着,他讨论了朱子对自然界的一些论述,比如对物质层面的天地的看法、对万物的看法(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对人的物理、精神、生理各方面的理解。最后,他从与中西方科学传统出发,考察朱子的自然哲学概念和对自然界的论述,比较二者的异同。
金永植在2009年发表的《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①一文中指出,朱子对“自然科学”(天文、历法、医学)和“超自然主题”(如,占卜、风水、内丹、祭祀,等等)均有大量研究,认为它们既是他“格物”学说的体现,又是出仕儒者需要涉猎的课题(因为它们可以增进百姓社稷的福祉)。金永植的文章从以下三方面讨论了朱子对科学和超自然主题的研究:第一,朱子对当时流行的文本做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和注疏,编辑相关著作、确立正确意义、校正错误甚至更动原文,并确立学者应研习的最佳读本。第二,朱子赋予超自然主题以合理性,认为它们并不违背儒家的基本立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气”的概念以及气与心的交互作用为这些超自然主题提供了理据,比如,内丹和风水等技术之所以养生,乃是因为“气”本身的生命特质以及心对人体外阴阳之气的掌控能力,另外,卜筮和祭祀中还涉及人心与天地之气或祖先之气的相互感通。其次,朱子批评同时代的儒者专研《易经》的义理而忽略其占卜面向,指出《易经》卜筮是一种重现宇宙过程的活动,《易经》是联结人体与宇宙运转的主要工具,而占卜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转。第三,朱子对当时超自然的奇异事例时保持开放态度,但将它们归因于气的性质和活动,而不是直接承认有超自然的存在体与力量。金永植还分析了朱子的这种开放态度的产生原因:朱子对智力挑战的兴趣、朱子对自己在许多学科上的卓见自信,以及朱子对古代知识的一贯尊崇。金永植最后总结说,由于朱子对科学与技术的主题给予了足够关注,使得儒学更为完备和开阔,并具有了科学精神;同时,朱子对超自然主题的涉猎,也相对缓和了他的理性主义立场,同时使他的哲学体系更为完备和富有解释力。
梁承武的博士论文《朱子哲学思想之发展及其成就》(1984)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本。该书以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义理内容为中心,讨论了先秦、北宋儒学与朱子思想的师承关系、朱子关于中和问题的论定、朱子关于仁说的论辩、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及理气论以及朱子哲学可能为现代哲学讨论贡献的话题,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该书是当代韩国学界为数不多的对朱子本人的哲学思想予以全面述评的专著,但是从内容上说,这本书却没有太多新的建树,基本上未超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朱子的判教。
(五)小结。
综观之,当代的朝鲜朱子学界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相比于对朱子本人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当代朝鲜朱子学界更重视对朝鲜历史上的朱子学研究大家的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其二,相比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传统社会拥有的绝对影响力和权威地位,当代的朝鲜朱子学乃至儒学已经萎缩,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文化思潮之一。其三,与朱子学的地位变化相伴随,在朝鲜李朝时期成果迭出的对朱子学中的理气心性及人物之性同异等思想的探究和发展,被客观的思想史研究以及为朱子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寻求根基的探讨所替代。
这三个特征在当代朝鲜朱子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有体现。20世纪初,朝鲜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论派和调和论派的学者大都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运用朱子学著作的理论为现实困境找出路。1905—1945年的日本殖民时期,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朝鲜传统文化岌岌可危,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多运用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以道统为己任,使自身心灵融入朝鲜朱子学的血脉,张志渊、何谦镇等朱子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中均有很强的道统意识,致力于延续朝鲜朱子学命脉,且他们本人也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实践传统文化。1945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朱子学的情势虽不及日本殖民时期的灭顶之灾,却仍十分严峻,主要原因之一乃是韩国社会对于朱子学的文化价值产生了质疑。这一情形与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出现的朱子学危机多有类似之处,于是,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也就类似于20世纪初的朱子学研究,即说明朱子学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决定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在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嗣后,复兴传统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朱子学面临的危机逐步缓解,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多样化,但是,韩国社会的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子学权威地位不再的事实,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转而以客观的史学研究和训诂考据研究为主(虽然偶有义理分析的研究著作,却毕竟不是主流),缺乏新的理论建树。
朱子学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传入朝鲜,经过高丽王朝时期100多年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到14世纪末成为朝鲜李朝的建国理念(即官方哲学),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对此后500余年间朝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期,为朱子学的初传阶段。嘉定十七年(1224)春,朱熹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等到达高丽全罗道的锦城,建立书院讲学,传播朱熹思想,这是朱子学在朝鲜民间传播之滥觞。而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引起统治者重视的则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安垧、白颐正等人。安珦(1243—1306)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朱子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教之正脉,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横经受业者动以百计”。③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④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1298年随忠宣王到元大都燕京,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大量程朱理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珠(颐正)。”①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颇有建树。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
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之所以会在此时传入朝鲜,一方面与高丽同元朝的密切关系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有关。可以说,正是朱子学北传并在元朝取得统治地位,加之高丽同元朝频繁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为朱子学流入高丽疏通了渠道,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程朱理学在中国产生时,汲取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适应了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也为其移植朝鲜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二是14世纪下半期,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阶段。安珦、白颐正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更多地还只是停留在对程朱理学著作的介绍和引进上,还来不及对程朱理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挥,而且传播的规模尚局限于高丽上层极狭小的范围内。进入14世纪下半期,由于朱子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李朝开国后朱子学正式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推动朱子学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
李穑(1328—1396)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李齐贤(1287—1367)是权溥的女婿,曾跟随忠宣王滞留元大都30年,其学注重程朱的“敬以直内”,反对佛教和汉唐经学。李穑年轻时,曾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学者皆仰慕。掌国文翰数十年,屡见称中国”。③官至宰相。他在成均馆任大司成期间,以朱子学为教育内容并对《小学》作谚解,进行普及,任宰相期间,笃力推行儒学教育,在中央建五部学堂,地方设乡校。史载:恭愍王十六年(1367)“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威,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土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月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尘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①后来对朱子学有创见发挥的学者如郑道传、极近等,多出自李穑门下。
郑梦周(1337—1392)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②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③他对朱子学的阐发,同代人颇为折服。“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④李穑曾高度评价郑梦周:“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⑤
郑道传(1337?—1398)号三峰,他不仅是高丽两班改革派的干城,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他“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鸣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邪说,明天理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⑥权近(1352—1409)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受到郑道传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论。权近的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五经浅见录》是继承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李朝时期刊行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溯其发端盖出于权近的《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更是远及日本。
这一时期的高丽朱子学,正是经过李穑、郑梦周、郑道传及权近等的大力推动,加之它适应了当时改朝换代的社会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新王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李朝(1392—1910)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1392年李朝开国。李朝统治者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李朝开国到1876年日本势力入侵朝鲜的近500年间,朱子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甚至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也只有借助朱子学的外衣才能存在。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为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到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退溪学的代表人物李滉(1501—1570),字景浩,号退溪,是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退溪集》(68卷)、《朱子书节要》、《启蒙传疑》、《心经释象》、《天贫图说》、《四端七情论》等。李退溪终身尊信朱熹的思想和学问,武夷山是朱熹晚年弃官隐居和沈潜学问的地方、陶山是李退溪隐居的地方,自古以来又叫作武夷。1183年4月,朱熹54岁时,在武夷山建盖了精舍,翌年写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因物寄兴,沿着武夷山的九曲描写了名胜和景物特色。退溪阅读了《武夷山志》之后,从想象中游览了朱熹隐居的武夷九曲,继承了朱熹《武夷棹歌》的形式,写了《次武夷棹歌》十首,引端了后来韩国各地指称九曲的潮流。如18世纪后期李野淳等人进行的陶山九曲的设定和有关诗歌的创作,他的《陶山九曲》诗次韵朱熹的《武夷棹歌》,又把李退溪的《次武夷棹歌韵》的意向当基础,描写了陶山一带的山水风光。退溪的《武夷棹歌》和韵不仅形成了韩国诗歌史的传统脉络,而且退溪学派的人往往把陶山九曲看成想象武夷和学习朱子的体验空间。①在哲学上,李退溪直宗朱熹,持“理一元论”观点,主张理贵气贱说和理气互发说,重视实践意义的“敬”,强调世界万物产生于“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动静乎”。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先知后行”,强调“性”有纯善无恶的“本然之性”和善恶不定的“气质之性”之区别,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启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之先河。其所创建的陶山书院,至今仍是韩国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书院。退溪学目前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由首尔退溪研究院创办于1973年的《退溪学报》,至今已经发行了一百多期。由退溪学釜山研究院创办的《退溪学论丛》至今也已发行了十余辑。退溪学国际会议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以上。韩国首尔和釜山、日本东京和福冈、中国北京以及香港和台北等城市都曾主办过研讨会。退溪性理学、退溪诗学等相关专题的研究始终都是学界的热点。
这一时期朝鲜朱子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李珥。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世称栗谷先生。1558年去陶山拜李混为师。1564年考中生员、进士科和明经科,历任户曹佐郎、吏曹佐郎、户曹判书、大提学等官职。在因病辞官期间,他回到地方专心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著有《栗谷全书》44卷。李珥反对“理气互发论”,主张“理气兼发论”,创立了朝鲜朱子学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他认为世界是由“气”和“理”所构成,“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理气“浑沦无间”,“实无先后之可言”,同为世界万物之源。但他又认为如论理气先后之分。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官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反对李滉在“性”“情”上的“四七说”,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认为七情以外无四端。李滉、李珥的“四七论争”,开拓了朝鲜朱子学的新领域,后与李滉一起并称为朝鲜思想界的“双璧”“二大儒”。
以李滉为中心的岭南学派(主理派)和以李珥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气派)的论辩持续了长达三百年之久,而这也是朝鲜朱子学的成熟期和巅峰期。到了16世纪末,朱子学逐渐从学术论辩转到与理论研究无关的“礼论”等问题,甚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党争工具。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畿湖学派分化为“老论”和“少论”。“老论”学者将朱子学化为绝对理念,并以自己的理论为朱子学正统。“少论”学者则反对朱子学绝对化甚至批判朱子学,还出现了郑齐斗(霞谷,1649—1736)这样的朝鲜阳明学大家。与此同时,岭南学派中则出现了“实学”之风,从“利用厚生”的观点来批判观念化的朱子学,谋求儒学的新方向。如以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的“实事求是学派”,主张在研究经典时依确实的考证,理解文本真正的意义;以李翼(星湖,1681—1763)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关心土地制度和行政改革)和以朴趾源(1737—1805)为中心的“北学派”(振兴农业、主张工商业的流通和生产技术革新)则主张理论研究要对现实社会的文物制度和社会文化政策有贡献。实学派观点的集大成者是丁若镛(茶山,1762—1836)。他主张土地和社会制度改革,重视科技,这既使朝鲜从性理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也间接加速了朱子学在朝鲜的衰落。
二 当代韩国的朱子学的研究
(一)20世纪初的朝鲜朱子学。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面对西学的渗入,朝鲜朱子学内部分化为传统论派、开化论派和调和派。三派的思想特点及其研究方法大致如下。
传统论派开展卫正斥邪运动,有原教旨主义的特点,大都奉行尊华攘夷的义理思想,秉持朱子“理尊气卑”的形上学,视儒学为理、为王道,西学为气、为霸权主义。按照朝鲜朱子学思想体系的两大派——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①——来划分,岭南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震相(号寒州,1818—1885)、张福枢(1815—1900),畿湖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柳麟锡、田愚(号艮斎,1841—1922)、朴世和(1834—1910)等②。由于我们的关注点是当代朱子学,这里将略去对几位19世纪的传统论者思想的考察,而关注柳麟锡、田愚这两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论者的思想。
柳麟锡主张,儒者在国家变乱之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态度:第一,发起义兵以扫清逆党;第二,即使离开国土,也要守住旧制度;第三,奉献生命以遂成其志。③他的理论依据是理尊气卑、理主气客的思想。他指出,“其所本者理,所形者气,而理气元是帅役上下”①。但他的兴趣点并不在讨论理气的关系,而在于以此为依据,强调民族自主和确立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批判当时朝鲜的西化倾向。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五伦”乃是据于天理,而西方的新教育则只是追求形气以满足欲望,因此是应当拒斥的。另外,西方新教育的推行是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之一,所谓的西化不过是日本希望引导朝鲜脱离清室、逐步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实现韩日合并的奸邪诱饵。
类似地,田愚的研究也是将性理学作为理论基础,而着眼于解决当时韩末的社会危机。不过,他的性理学主张与柳麟锡的有冲突。在《两家心性尊卑说》(1918)一书中,田愚指出了他的性理学主张与其他学派的主张的不同:他主张“性理心气论”,认为心是气而不是理,因为心并非静而无为,而是动而有为的;相比之下,其他学派则主张心主理,而没有看到心须依理合理才能无偏失的道理。在此基础上,田愚在《从重时中辨》(1905)一文中指出,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体现“性即理”说,而夷狄和异端则只能随“心即气”的欲望思考和行为②。与此相呼应,田愚在《与郑君祚》(1877)③、《论裴说书示诸君》(1908)④等一系列书信中提出,应对当时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当权者作性理学的内圣修养,并施行排斥夷狄之开化论的政策。随着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加剧,田愚选择了隐遁守旧而力保华脉,将余生奉献给了朱子学乃至中华文化的教育和写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论派主要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即他们对朱子思想和著作的讨论是以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为旨归的。
再来看开化论派。秉持开化论的学者们⑤积极接受西方新学(主要是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进化论),批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的无用性,提倡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甚至将被日本殖民的亡国原因归咎于儒学,以为朱子学空谈心性,阻碍智力发展,并以腐朽思想求生存,实乃缘木求鱼①。
最后来看调和派。调和派由一些活跃于政界的儒者组成,提倡以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体新用论或儒体西用论,反驳开化论对儒学的批判,认为开化不是无条件地仿效西方,而是要适合自己社会的现况。这一派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如朴殷植、金允植,等等)是韩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②。调和派鲜有朱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是持批判朱子学的立场的。其中,朴殷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朴殷植在早年(1859—1897)属于传统论派,仅以朱子学为正学。在经历了甲申政变(1884)、清日战争、甲午更张(1894)等事件之后,朴殷植看到了传统论派在对抗日本侵略上的无力性,遂转而批判朱子学。他一方面创立“大同教”(1909),作为儒家改革的主体;另一方面,推广阳明学,批判朱子学。在《儒教求新论》(1909)一文中,朴殷植指出了朱子学的三大弊病:第一,朱子学只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工具,与儒家的根本政治思想(民本主义和大同主义)相背离;第二,朱子学只是消极布教的权威主义而已,偏离了孔子周游列国思以易天下的理念;第三,就学问本身来说,朱子学支离繁杂,所讲的“知”与新学的科学之知是同一知识层次;而阳明学的良知则高于科学知识,可以吸收各种科学,纳于良知之学内。③类似于传统论派,朴殷植也同样运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只是他的通经致用方法是从批判朱子学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朱子思想,比如,将朱子学在现实运用中的教条化归咎于朱子思想本身,并将朱子的“知”等同于闻见之知。
(二)1905—1945年的朝鲜朱子学。
1905—1945年期间,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朱子学作为朝鲜本国文化传统的代表而遭到了歪曲①甚至废止,这令20世纪初传统论派的复兴朱子学努力严重受挫。朱子学乃至儒家文化都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处于低谷期。尽管如此,一些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却仍致力于延续朱子学和儒学的命脉。这段时期内比较著名的朱子学和儒学成果有: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何谦镇的《朱子書節要》(1939)、《东儒学案》(1943)。
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是韩国首部近代儒教通史。张志渊曾任《时事丛报》《皇城新闻》的主笔,并在满洲条约签定时,发表社论《是日也放声大哭》(1905),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在《朝鲜儒教渊源》一书中,他受到韩国实学的影响,将奉行朱子学抽象理论的性理学家斥为小人儒,与他所推崇的李翼(星湖)、丁若镛(茶山)等君子儒区分开来,认为朝鲜李朝衰亡原因是因未用君子儒或真儒。他既批评传统论派不知变通、拘泥于性理和训诂,又批评开化论派不懂得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盲从西学之浅表,认为二者均失其中,主张儒教伦理与近代科学可以参互变通。他表示,西方的科技是近三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故论古代文明,则东方优于西方,只是旧儒们拘泥固执,而使儒学浮虚无灵,才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衰落。
何谦镇(1870—1946)堪称以道统为己任的典范。他本人曾以儒者身份参与独立运动,并两次入狱,并于1931年创立“德谷学堂”,晚年著书立说,致力培养后学。他的《东儒学案》(1943)可以算作朝鲜儒学史上唯一的学案。朝鲜儒学史上类似的著作是朴世采的《东儒师友录》(1682)和宋秉瑄的《浿东渊源录》(1882),但在影响力上皆不及《东儒学案》。《东儒师友录》包括了薛聪以下的750位学者,但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他们的师友渊源和行迹的,而不是关于思想。另外,这些被选择的人物大都是畿湖学派的学者,时代也局限于18世纪后期。《浿东渊源录》参照了朱子《伊洛渊源录》的体例,兼参《东儒师友录》,主要记述人物的思想渊源,多引用关于人物行迹的材料,而不是人物的思想观点,且未区分学派。相比之下,《东儒学案》则要全面很多。《东儒学案》分为上、中、下三册二十三篇,每个学案里,都包括学派来源、代表学者的生平和学问特性、思想特色等内容。何谦镇以道统论的观点成书,认为理学为儒学正统,并以朱子学为理学正统,以退溪学派为中心。尽管本书重视道学义理实践、而不注重性理学的哲学理论和各学派的学问异同,从而未论及朝鲜阳明学派(江华学派),但是全书对各个理学学派的分殊和脉络均有细致而公允的分析和评价,这使得此书的分类构图一直为人所称道,也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不失为研究韩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一项重要参考文献。
(三)20世纪40—70年代初的朝鲜朱子学。
1945年之后,朱子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处于低谷期。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在经历了促进韩国近代化进程的甲午更张运动以及日本实行的彻底抹杀韩国传统文化的政策之后,中断的文化传统已很难迅速复苏。第二,光复之后的韩国处于文化过渡期,而朱子学没能通过自我改革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力与其他各类文化竞争,当然也不能主导韩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三,美国军政时期(1945—1948),西方文化渗入,致使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很难一枝独秀,韩国民众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很难对朱子学有亲近感,加之韩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逐渐西化,仅有极少数韩国大学维持朱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命脉。第四,韩国政府和民众都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富裕上,进一步造成了传统伦理价值的危机。第五,在经历朝鲜李朝崩坏、日本殖民统治之后,20世纪的韩国基本上每十年有一动荡,50年代南北对峙、60年代学生民主革命和军事政变、70年代实施巩固维新独裁体制,韩国社会处于长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中,这对于20世纪初就岌岌可危的韩国朱子学来说,无疑又是新的挑战。特别是50年代的南北对峙以及60年代实学思想的复兴(克服朝鲜朱子学空谈心性的倾向,力求回到原始儒学的质朴面貌,兴起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都是对朱子学研究的阻碍。
1945年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论著有:玄相允《朝鲜儒教史》(1949);李丙焘《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1959)以及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郑寅普、李相殷的著作。
玄相允的《朝鲜儒教史》采用文本考据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朝鲜朱子学两大富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对峙为主线,勾画出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脉络。李丙焘的《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则采用了史学研究方法,考察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朝鲜的发展轨迹,着重于梳理这两派在朝鲜的历史流变,而不是进行思想分析和论述。
郑寅普和李相殷的著作可以被看作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两大思想体系——阳明学现代新儒学和朱子学现代新儒学——之间的争论的绝佳范本。同为韩国现代新儒家,两大思想体系皆主张兼采东西学术之长,综合新旧之学,但对何为东方学术之长的问题有争议。郑寅普著有《阳明学演论》①,继承了20世纪初的朝鲜阳明学家朴殷植的批朱立场,认为阳明学与朝鲜民族意识能自然结合,圣贤之道在于人心未亡,而其人情自身则是至善良知的表现;而朝鲜儒学流弊则生于朱子学,朱子学或讲论心性而少于己身的良心契合,或标榜道义却以此图谋私利②。李相殷则是朱子学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他著有《〈大学〉〈中庸〉之现代的意义》《再论东洋文化》《从humanism看儒教思想》《批判国史教科书之性理学叙述》《儒学与韩国思想》③《四七论辩及对说、因说的意义》④等,旨在匡正对朱子学的流俗偏见,并试图熔铸朱子学与现代学问。类似郑寅普,他也提倡修正儒学重义轻利、内本外末的思想,主张兼顾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但他认为朱子学的性理之学并不像阳明学者理解的那样与现实生活相疏远,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的,从而实学并不与性理之学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无实学之性理学为空虚,无性理学之实学为盲目也。”⑤具体说来,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当今价值在于三方面,其一,看到制度的制定和改革并非万能,制度操作者的道德性更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教义是基础;其二,西方的历史呈现出对立分裂形态,而儒家则提示出一条合作、统一之道,比如,秦、汉统一就与儒家的政治哲学经典《大学》和心性哲学经典《中庸》的出现关系密切;其三,肯定朱子对《大学》的格物释义,认为其具有科学精神,可以视为清代实学和韩国实学的鼻祖,朱子学较之陆王学,具有更踏实的学风和现代意义。
(四)多元化时期的朝鲜朱子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韩国社会的国际化,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开始流行,其中不乏正视传统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在各个大学重视复兴传统文化、增加研究人员以深化学术研究的风潮推动下,为朱子学的复兴带来了新的生机。韩国学界甚至兴起了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并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韩国学者梁承武(2008)的统计,从80年代开始,有关朱子学方面的单行本、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等各类论著较80年代前有了极大增长,而研究广度也极大提升①。就广度来说,这些研究涉及了朱子及朝鲜历代朱子学大家的哲学思想(以理气论、工夫论等方面的研究业绩较为丰厚)、散文和诗歌研究、教育思想,等等。然而,从研究的深度来说,70年代之后的朱子学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大多数研究都缺乏思想上的创新意识,而以客观、逻辑性的思想史研究或文本研究为基本特征,即只停留在研究朱子和历代朱子学大家的思想、论著和言行的层面,把儒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从70年代至今,涉及韩国朱子学史研究的论著及论文主要有:裴宗镐《韩国儒学史》(1974)②、《韩国儒学资料集成》(1980),李东俊《关于17世纪韩国性理学派历史认识的研究》(1975)③,韩永愚《朝鲜前期性理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1976)④,柳承国《韩国的儒教》(1976)、《东洋哲学研究》(1983)⑤、《韩国儒学史》(1989)⑥,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1980)⑦、The Korean Controversy over ChuHsi's ViewontheNatureofMan and Things(《韩国学界关于朱熹论人、物之性的争论》,1982)①、《东洋思想与韩国思想》(1984)②、《退溪李滉的哲学思想》(2000)③,权延雄《世宗朝的经筵和儒学》(1982)④,李楠永《理气四七论辩与人物性同异论》(1984)⑤,琴章泰、高广稷《儒学近百年》(1984)⑥,金忠烈《高丽儒学史》(1984)⑦、《韩国儒学史》(1998),李成茂《朱子学对十四、十五世纪韩国教育及科举制度的影响》(1986)⑧,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 (1986)⑨、 《韩國儒学史》 (1987),玄相允《韩国儒学史》(1986)⑩,崔英辰的五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史》(1997),姜在彦《韩国儒学两千年》(2003),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室编的七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大系》(2005—2007),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2008)⑪,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2011)⑫,等等。其中也不乏研究韩国大儒的思想的论著,如韩永愚《郑道传思想研究》(1983)⑬,李东翰《技术之危机与敬哲学之解答》 (1988),申龟铉《西山真德秀之〈心经〉与退溪李滉之心学》(1988),李基东《李退溪的人道主义和敬》(1988),丁淳睦的《朱晦庵和李退溪之书院教育论》(1988)⑭。还有一些是比较韩国儒学与其他国家儒学研究状况的论著,如,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1995)①。
这些论著主要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梳理朱子学在朝鲜的发展脉络(或某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或者横向考量朝鲜朱子学研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朱子学研究之间的异同。比如,裴宗镐(1974)探讨了朝鲜性理学的主要议题——四端与七情论辩及理气论争——的演变过程及论争的焦点所在;柳承国(1976,1989)探讨了朱子学传入高丽的经过以及朝鲜性理学的兴盛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尹丝淳(1980,1984)则以对韩国儒学的特性为分析主线,探讨了韩国神话传说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的权威地位的关系(他认为,韩国神话传说揭露出韩国文化对于超越问题的兴趣,使得性理学家对于朱子学中的“天命”“天人合一”“穷理”等问题有细致的、突破性的讨论)、朝鲜前期和后期思想家对于“实学”和“虚学”的看法的不同(朝鲜前期儒者以佛学为虚学、性理学为实学,后期实学派则以超越训诂和辞章、袖手谈心性的性理学为虚学,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之学为实学),等等。有时,这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以客观叙述为旨归的,而是带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这种研究带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论预设,比如,金忠烈(1984,1998)的儒学史叙述是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儒学并非宗教,不认同来世,而是追求现世的现实主义;而琴章泰(2011)则主张,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并从朝鲜历史上积极实践儒学价值的儒学家的具体功绩研究入手(比如张志渊、何谦镇等儒者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奔走、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等),研究儒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第二,这种研究方法是与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比如,李东翰(1988)、申龟铉(1988)、李基东(1988)、丁淳睦(1988)都是试图通过将研究退溪思想与探讨其现代意义结合起来,为现代社会确立价值目标。不过,从总的研究倾向上来看,大部分采用史学研究方法的论著还是从客观的角度切入的。
除了对韩国朱子学史的研究,70年代之后的韩国朱子学研究也涉及对朱子本人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训诂考据的方法;二是义理研究的方法;三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了训诂考据方法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朱子论著的韩文注译工作。根据梁承武(2008)的考察①,在韩国出版发行的朱子学译著主要有《四书集注》、《小学集注》、《诗集注》②、《朱子家礼》③、《朱子家训》④、《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到卷六“性理三”部分⑤、《近思录》⑥,等等。至今,尚无朱子全套著作的完整韩注本问世,甚至一些朱子的重要著作(如,《四书或问》《仁说》,等等)亦未有韩注本。
运用了义理研究方法的朱子学研究代表作是金永植(Yung SikKim)的一系列朱子学著作。由于他的研究以往较少被讨论到的朱子自然哲学为关注点,发前人之所未发,笔者拟用一定篇幅介绍他的研究内容。
金永植在2000年出版了专著TheNatural Philosophy ofChiHsi(1130—1200)(《朱熹的自然哲学1130—1200》)⑦,研究朱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将朱子的自然哲学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相比较。他首先讨论了朱子自然哲学中的基本概念——理、气、阴阳、五行、象数,等等,并兼论鬼神、天和圣人这些虽“不属于自然世界、但仍与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有关”⑧的事物。接着,他讨论了朱子对自然界的一些论述,比如对物质层面的天地的看法、对万物的看法(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对人的物理、精神、生理各方面的理解。最后,他从与中西方科学传统出发,考察朱子的自然哲学概念和对自然界的论述,比较二者的异同。
金永植在2009年发表的《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①一文中指出,朱子对“自然科学”(天文、历法、医学)和“超自然主题”(如,占卜、风水、内丹、祭祀,等等)均有大量研究,认为它们既是他“格物”学说的体现,又是出仕儒者需要涉猎的课题(因为它们可以增进百姓社稷的福祉)。金永植的文章从以下三方面讨论了朱子对科学和超自然主题的研究:第一,朱子对当时流行的文本做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和注疏,编辑相关著作、确立正确意义、校正错误甚至更动原文,并确立学者应研习的最佳读本。第二,朱子赋予超自然主题以合理性,认为它们并不违背儒家的基本立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气”的概念以及气与心的交互作用为这些超自然主题提供了理据,比如,内丹和风水等技术之所以养生,乃是因为“气”本身的生命特质以及心对人体外阴阳之气的掌控能力,另外,卜筮和祭祀中还涉及人心与天地之气或祖先之气的相互感通。其次,朱子批评同时代的儒者专研《易经》的义理而忽略其占卜面向,指出《易经》卜筮是一种重现宇宙过程的活动,《易经》是联结人体与宇宙运转的主要工具,而占卜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转。第三,朱子对当时超自然的奇异事例时保持开放态度,但将它们归因于气的性质和活动,而不是直接承认有超自然的存在体与力量。金永植还分析了朱子的这种开放态度的产生原因:朱子对智力挑战的兴趣、朱子对自己在许多学科上的卓见自信,以及朱子对古代知识的一贯尊崇。金永植最后总结说,由于朱子对科学与技术的主题给予了足够关注,使得儒学更为完备和开阔,并具有了科学精神;同时,朱子对超自然主题的涉猎,也相对缓和了他的理性主义立场,同时使他的哲学体系更为完备和富有解释力。
梁承武的博士论文《朱子哲学思想之发展及其成就》(1984)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本。该书以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义理内容为中心,讨论了先秦、北宋儒学与朱子思想的师承关系、朱子关于中和问题的论定、朱子关于仁说的论辩、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及理气论以及朱子哲学可能为现代哲学讨论贡献的话题,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该书是当代韩国学界为数不多的对朱子本人的哲学思想予以全面述评的专著,但是从内容上说,这本书却没有太多新的建树,基本上未超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朱子的判教。
(五)小结。
综观之,当代的朝鲜朱子学界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相比于对朱子本人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当代朝鲜朱子学界更重视对朝鲜历史上的朱子学研究大家的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其二,相比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传统社会拥有的绝对影响力和权威地位,当代的朝鲜朱子学乃至儒学已经萎缩,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文化思潮之一。其三,与朱子学的地位变化相伴随,在朝鲜李朝时期成果迭出的对朱子学中的理气心性及人物之性同异等思想的探究和发展,被客观的思想史研究以及为朱子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寻求根基的探讨所替代。
这三个特征在当代朝鲜朱子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有体现。20世纪初,朝鲜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论派和调和论派的学者大都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运用朱子学著作的理论为现实困境找出路。1905—1945年的日本殖民时期,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朝鲜传统文化岌岌可危,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多运用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以道统为己任,使自身心灵融入朝鲜朱子学的血脉,张志渊、何谦镇等朱子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中均有很强的道统意识,致力于延续朝鲜朱子学命脉,且他们本人也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实践传统文化。1945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朱子学的情势虽不及日本殖民时期的灭顶之灾,却仍十分严峻,主要原因之一乃是韩国社会对于朱子学的文化价值产生了质疑。这一情形与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出现的朱子学危机多有类似之处,于是,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也就类似于20世纪初的朱子学研究,即说明朱子学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决定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在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嗣后,复兴传统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朱子学面临的危机逐步缓解,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多样化,但是,韩国社会的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子学权威地位不再的事实,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转而以客观的史学研究和训诂考据研究为主(虽然偶有义理分析的研究著作,却毕竟不是主流),缺乏新的理论建树。
附注
②文中所说的韩国朱子学研究指的是朝鲜半岛(包括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的朱子学研究。
③《高丽史》列传卷十八。
④《高丽史》列传卷十八。
①《高丽史》列传卷十九。
②《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③《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八。
①《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八。
②《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③《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④《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⑤《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⑥《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①林鲁直:《退溪学派的〈武夷棹歌〉受容和陶山九曲》。
①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形成于16世纪,前者是主理派,尊奉李退溪的思想体系,后者是主气派,尊奉李栗谷的思想体系。
②参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第84页;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23—324页。
③参见《毅庵集·散言》,卷二十七,杂著,乙未十一月。
①参见《毅庵集·散言》卷二十七。
②参见《秋潭别集》卷三,第36—37页。
③参见《秋潭别集》卷二,第7页。
④《秋潭别集》卷三,第2页。
⑤开化论派的主要代表是金玉均(1851—1894)、徐载弼(1866—1951)、朴泳孝(1861—1939)。
①李光麟:《旧韩末新学与旧学之论争》,《韩国开化思想研究》,肃兰市:潮阁1992年版,第205—206页。
②这也被认为是韩国现代新儒家的理念。参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第87页。
③参见《朴殷植全书》下卷,第44—47页。
①以日本学者高桥亨为代表。他从殖民史观出发,著有《朝鲜儒学史大纲》(1925)和《在朝鲜儒学史的主理派与主气派的发展》(1929)二书,宣扬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正当性。
①三省文化财团1972年版。
②参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第97页。
③均收录于《李相殷先生全集》。
④载《亚细亚研究》,高丽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3页。
⑤李相殷:《儒学与韩国思想》,《李相殷先生全集》(韩国哲学Ⅱ),第121页。
①参见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第45—47页。
②延世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③成均馆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75年版。
④载《韩国思想大系》,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6年版,第80—91页。
⑤槿域书斋1983年版。
⑥傅济功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⑦玄岩社1980年版
① Chan Wing-tsit ed.,ChuHsiandNeo-Confucianis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570-583。本文讨论朝鲜李朝朱子学史上最大的两大争论之一——人、物之性是否相同(另一个争论是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辩),肇始于李朝大儒韩元震与李东之间的论辩。
②乙酉文化社1984年版。
③国际退溪学会2000年版。本书介绍了韩国性理学大儒李退溪的生平和哲学(包括理气论、心性论、敬学)、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当代意义,等等。
④载《世宗朝文化研究》,博英社1982年版。
⑤载《韩国思想》,烈音社1984年版。
⑥博英社1984年版
⑦高丽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⑧杨秀枝译,《韩国学报》,1986年第6期,第169—188页。
⑨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
⑩汉城:玄音社1986年版。
⑪《杭州师范大学学报3.2》(2008),第45—47页。
⑫韩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⑬首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是关于高丽末期大儒郑道传(号三峰,1342—1398)的生平、著述、思想的综合研究成果。
⑭这几篇均是第九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参见高令印《国际朱子学研究的新动向》,邹永贤主编:《朱子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①刘李胜、李民、孙尚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①参见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第48页。
②这三本集注均是由成百晓翻译、民族文化研究会出版的。
③任敏赫翻译。
④赵敦相、崔载铉翻译。
⑤许铎、李尧圣译注,清溪出版社出版。
⑥弘益出版社。
⑦ Yung Sik Kim.TheNaturalPhilosophy ofChiHsi(1 130—1200).Philadelphia: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2000.
⑧Ibid..
①金永植:《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15—24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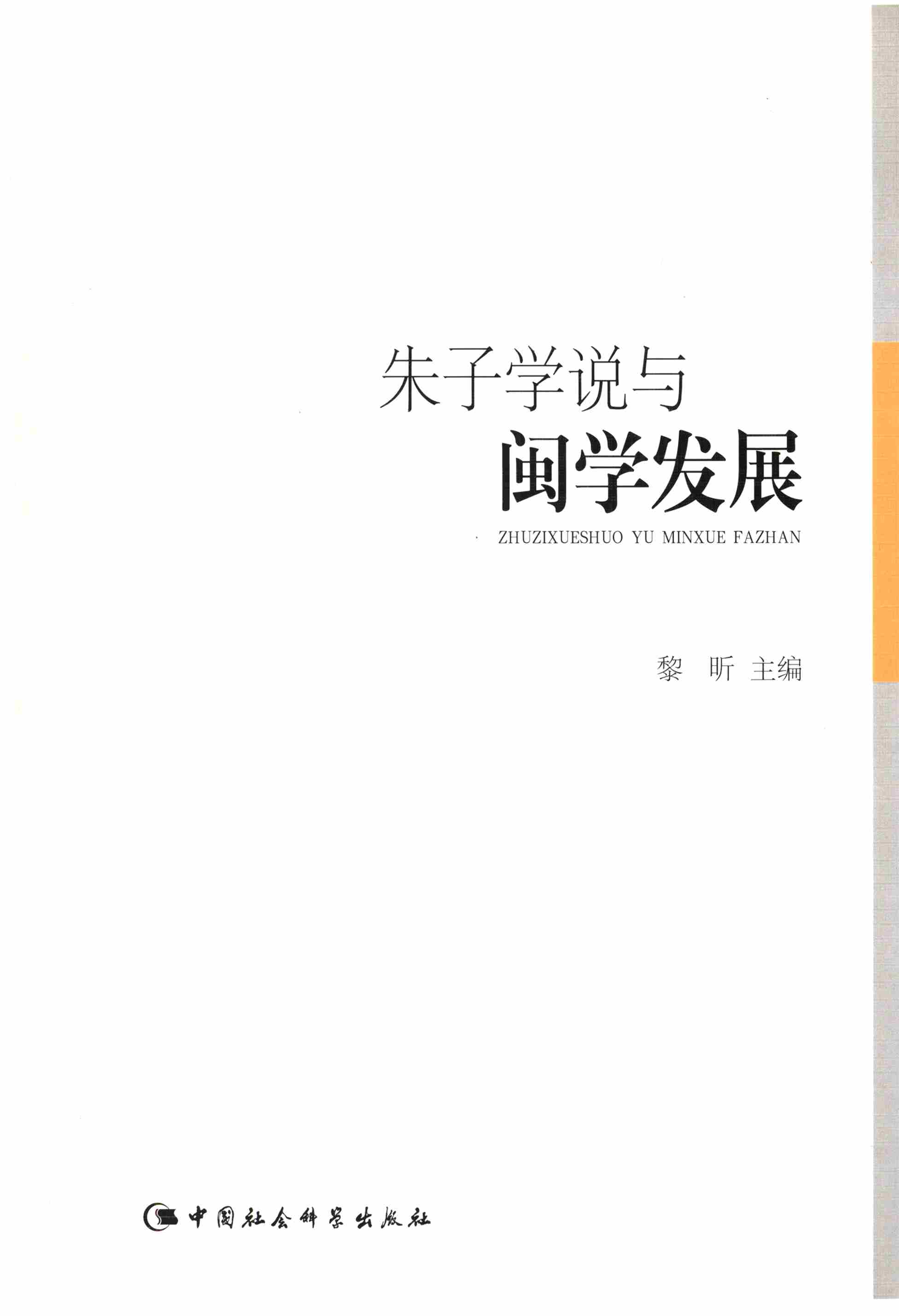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八章,主要包括福建历史文化发展与闽学的产生、朱子学说与闽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传承、朱子学说与闽学思想的基本内核、朱子学说与闽学的社会教化论、朱子学说与闽学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等内容。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