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外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755 |
| 颗粒名称: | 第七章 国外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49 |
| 页码: | 174-222 |
| 摘要: | 本章主要探讨了国外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文章首先介绍了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分析了这些地区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特点和贡献。然后,文章探讨了韩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分析了韩国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独特性和价值。 |
| 关键词: | 朱熹 闽学 研究 |
内容
朱子学自12世纪创建以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不断外渡,先后风靡韩国、日本,逐渐成为东亚世界的主流思想。虽然朱子学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欧洲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能作为一门独立学说获得长足发展①,在北美更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期,却最终在当代(尤其是20世纪中期之后)经由中西学者的不懈努力而最终获得了应有的关注。
第一节 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本节主要讨论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即20世纪以来该地区的学者对朱子的思想、著作、实践活动等方面加以研究的方法问题。尤以日本和北美这两处朱子学研究重镇为要,同时论及当代欧洲的朱子学。
管见所及,介绍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基本上都关注一阶(first-order)研究的成果,即基本上都以综述当代学者对朱子思想及实践活动的研究状况为目标,而极少涉及二阶(second-order)研究,即基本上不关注当代学者在进行朱子学的一阶研究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问题①。当然,朱子学方法论的这一研究缺憾并不表明方法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对于任何一个理论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发展前景,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方法论问题对于未来朱子学研究(无论海内还是海外)的走向和突破性成果的取得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有鉴于此,对当代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总结、分析和评价,就成为一种必要。
对“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方法的方法”问题,即如何确定某种方法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以方便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具体说来,这一问题涉及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按照什么标准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是按照研究时段分类、按照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分类、按照研究地区分类,还是按照研究著作的研究方法分类?其二,在特定的标准下,如何避免重复分类的情况?相较之下,按照研究著作分类所可能面临的质疑相对小于按照研究地区或按照研究者分类所面临的问题。按照研究著作进行分类的优势在于,每一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一般只有一个,依照每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将各个著作分门别类,可以较好地避免按研究者和研究地区分类时可能造成的难于判定所属类别的情况和重复分类的情况。所谓的主要研究方法,指的是在一本著作中最为核心的、让其他方法为之服务的方法。以日本学者后藤俊瑞的著作《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②为例。后藤在书中对“存养”“忠恕”等概念在朱子伦理思想中的作用做了义理分析,并辅以对这些概念的考证疏解。由此,义理分析方法是这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本文中的分类以研究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主要依据,适时参以研究时段、研究地区、研究者的分类,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著(包括论文)为例,对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讨论。又,文中所引英文,均为笔者译;所引欧洲论著及日文论著的原版书名、翻译及简介,分别参照了陈荣捷的文章The Study ofChuHsi intheWest(《朱子学在西方》)和石立善的文章《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①。
一 考证学的方法
儒家经解传统中的考证方法主要有声韵训诂和校勘考据两个面向。对于当代朱子学者而言,朱子的著作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经”的地位,当代对朱子著作的考证研究也恰契合上述两个面向的内涵,故笔者于此借用这两个面向对当代朱子学的考证学方法予以分类描述。
(一)声韵训诂的方法。
本文所说的声韵训诂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以通晓朱子著作的文句为旨,以克服因古今、中外之别造成的语言、文化理解上的隔阂。这种传统定义中的声韵训诂法在当代的日本和欧美朱子学界都有其代表著作。
当代日本朱子学以运用传统声韵训诂方法见长。在对朱子著作的注译方面,日本学界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首屈一指的。从广度上说,日本学者注译的朱子著作包括了朱子的诗学著作、解经著作、论先贤著作、论文汇编、信札和语录集等;从深度上说,日本学者的译注在底本选择、字句翻译、文本形成背景、经典出处考证等方面大多极尽细致之功。在朱子诗学方面,比较出名的日译本有吹野安与石本道明的《诗集传全注释》(全九册)②和宋元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子绝句全译注》③。对朱子解经著作的日译本为数颇多,其中比较为学界称道的是汤浅幸孙的《近思录》日译本④,而比较流行的是吹野安与石本道明的《论语集注》日译本⑤、小泽正明的《朱熹集注论语全译》⑥以及中村璋八与古藤友子翻译的《周易本义》⑦。对朱子论先贤著作的日译本中,以梅原郁的《宋名臣言行录》的节译本①最受欢迎,另外还有进藤英幸的《伊洛渊源录》节译本②和高畑常信的《伊洛渊源录》选译本③。对朱子论文、信札、语录的汇编本的日译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友枝龙太郎的《朱子文集》选译本④、高畑常信注译的《延平答问》⑤、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⑥、市来津由彦的《朱熹〈朱文公文集〉跋文译注稿》⑦等⑧。
相较之下,运用训诂考据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是北美朱子学界的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块研究领域。这种薄弱性并不是指北美朱子学界缺乏训诂考据研究的精品之作,而是指专事训诂考据研究的朱子学著作为数甚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已故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先生的几部著作可谓其中的开山之作,另外,伽德纳(Daniel Gardner)也在这方面有精品之作问世。
陈荣捷是北美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研究的先驱。在北美学界中,他不但是首批系统阐述朱子思想的学者,也是最早以英文译注的形式在北美大力推阐朱子著作和其他中国经典文献的学者。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刊Sources of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诸源》)⑨,负责理学部分的陈荣捷摘译了《朱子全书》中关于理气、太极、天地、鬼神、人物、性命、心性、仁等内容的数十条段落⑩。1963年陈荣捷出版了大部头译作A SourceBookin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文献选编》)⑧,其中的第三十四章专论朱子,除译朱子四篇重要哲学短文之外,又选译了《朱子全书》中的二百四十七篇段落。1967年,陈荣捷又出版了《近思录》的英文译注本①,除将原文622条悉数译出之外,陈荣捷又选译了语类、文集、四书集注、或问等朱子书中的281条相关集评条目;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人和朝鲜、日本学者的评论数百条;书末更有附言详述《近思录》的编纂经过、《近思录》选语统计表、《近思录》选语来源考等内容②。这些译著内容之详尽、注解之精细,在20世纪的北美朱子学界可谓先驱之作。
如果说陈荣捷在朱子学的训诂考据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朱子全书》和《近思录》的著译,那么伽德纳在1990年出版的Learningto bea Sage: Selectionsfromthe Conversations of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学以成圣:朱熹语录分类选集》)③则是对《朱子语类》的著译精品。伽德纳在这本译著中选译了《朱子语类》第七到第十一章,并在译著的导论中讨论了朱子的文化使命感、读书之法和教学之法等内容,指出朱子读书、教学之法的核心乃是让学人于读经解经中自我发现(而不是以疏通经典文意为鹄的),进而自担延续道统的使命,这种学以成圣的读书法于今日读书人亦颇有启示意义④。
与陈荣捷相似,欧洲汉学界在朱子学训诂考据方面的贡献也主要集中于对《朱子全书》和《近思录》的译注,只是在译注的翔实和细致程度上不及陈荣捷的英文版本。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注本有:戴遂良(Léon Wieger) 教士的Textes philosophiques: Confuciisme,Taoisme, Buddhisme(《哲学文选:儒道释》)中的朱子章⑤,英国汉学家布鲁斯(J.PercyBruce)译注的《朱子全书》第42—48章①,巴黎大学博士庞景仁(PangChing-jen)对《朱子全书》第49章的法文翻译②,以及葛拉夫神父(Olaf Graf)对《近思录》的德译本③。
另一种声韵训诂法在当代日本学者的儒家经典译注中比较多见。日本学者在翻译其他中国古典文献时参考了朱子对相应文献的注解,旨在通过疏通朱子注解的方式达致对朱子所注的古典文献的理解。这是一种以通晓朱子文句为间接目的的方法,笔者也将它归入朱子学研究方法中的声韵训诂方法。在当代日本的注经之作中,运用这种声韵训诂法的名作有仓石武四郎的《论语》日译本④、本田济的《易经》日译本⑤、岛田虔次的《大学·中庸》 (1967)⑥以及赤冢忠、金谷治、俣野太郎分别出版的《大学》和《中庸》日译本⑦。仓石武四郎注译的《论语》在注释上完全参照了朱子的《论语集注》和《朱子语类》。本田济注译的《易经》以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刊本的《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注释上主要参照朱子的《周易本义》,并参以程颐的《伊川易传》。岛田虔次的《大学·中庸》(1967)⑧以朱子的《大学集注》和《中庸集注》为底本,注释上亦主要参照了朱子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朱子语类》,同时还援引了其他儒者的相关阐释①。赤冢忠、金谷治、俣野太郎三人分别注译的《大学》和《中庸》除依朱注外,还另参其他注本。赤冢忠的译本兼收了汉唐的古注②与朱子的新注③。金谷治的译本以朱注为主,另参以清儒王步青的《四书本义汇参》。而俣野太郎的译本中,《大学》部分全依朱注,《中庸》部分则以郑玄与孔颖达的古注为主④。
(二)校勘考据的方法。
在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中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并因目的不同而呈现两种面向。
第一种面向旨在确定朱子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因传抄印刷造成的多种版本中哪个本子可靠,并通过比较不同的本子来校正其中的错简衍文。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朱子学界对《近思录》的考证上。总体而言,当代的日本朱子学者大多以清儒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为底本。市川安司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对朱子《近思录》的日译本⑤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译本的校勘以江永的《集注》为底本,并校以叶采的《近思录集解》,在注解上又极尽细致之功,标出了《近思录》中各条目的出处和语句的出典,颇有参考价值。当然,也有少数的正统派继承了古代日本朱子学的传统,以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为校勘底本。如,20世纪40年代秋月胤继的《近思录》译本⑥。
第二种面向旨在对朱子解经所引典据加以分类考察,探究朱子对圣贤本意的发明。如,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1976)⑦。大槻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几乎所有的典据做了分类,将汉唐“古”注、宋人“近”注及朱子“新”注分门别类,以表明朱子优游涵泳圣贤本意的苦心。这本考证专著在出版同年即被台湾学生书局以中文版发行,毛子水在为本书中文版所作的序中盛赞其为“研究朱子学最为有用的书籍”①。
二 史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比较多见于日本和北美的朱子学著作中,致力探究朱子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梳理朱子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脉络(包括朱子一门的师承关系)、考察朱子的教育、交游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在当代大陆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多拘于哲学领域的时代,海外学者的这些史学研究方法无疑是颇为值得借鉴和参考的。这些史学研究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朱子学研究——乃至宋儒研究——中认为宋代知识分子专注于“内向偏转”、醉心于修养心性的成见,表明宋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朱子一般,积极关心参与政事和推进政治改革;同时,通过对朱子的思想及实践活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也为更好地还原和研究朱子思想的实态提供了依据。
北美方面,陈荣捷、谢康伦(Conrad Max Schirokauer)、余英时和他的弟子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这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实践活动背景做出了贡献。
陈荣捷在朱子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②:第一部是《朱子门人》(1982)③。陈荣捷在这本书中详细考察了朱子门人的人数构成、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学术贡献等,是朱子门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第二部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ChuHsi:Lifeand Thought(《朱熹:生平与思想》)④,其中收录了考察朱子投身书院教育和朱子宗教生活的两篇论文。第三部是他在1988年出版的文集《朱子新探索》①,其中收录了他考察朱子的生平、居所、衣着、游历、教学、交游友人等生活化事件的多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陈荣捷在ChuHsi:Life and Thought(《朱熹:生平与思想》)和《朱子新探索》这两部著作中,都于朱子的实践活动上颇费笔墨,这可能源于陈荣捷对1982年由他牵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朱熹国际会议的观感。参加1982年会议的学者既有当时中国哲学界的翘楚也有学界新秀,会议论文也颇具广度和深度,但是陈荣捷却在会议论文集ChuHsi andNeo-Confucianism②的编者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与会学者们“对朱熹的思想关注有余,却不够关注朱熹的个人生活”③。这就促使陈荣捷在之后的研究中努力填补这一研究空隙,发掘大量以往不被朱子学界注意的新材料,从而大大深化和细化了朱子研究的课题。
谢康伦的朱子研究也是就朱子论朱子的进路,只是他的史学研究大致拘于对朱子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考察,而不似陈荣捷那般对朱子的家事、居游等日常活动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正因为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谢康伦在研究朱子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方面用功很深,史料处理上也很细致,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献时断章取义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在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Thoughtand BehaviorofChuHsi(《朱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④中,除了参考《朱子文集》等朱子典籍,又遍参王懋竑《朱子年谱》、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等书,详细历述了朱子的政治活动(朱子辞仕致仕的经过及其政事)和政治理念(朱子的政论)。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发表了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A StudyinAmbivalence(《朱熹的政治生涯:一个两难的问题》)⑤,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The CondemnationofWei-hsueh(《受攻击的理学:质疑伪学》)①和ChuHsi's PoliticalThought(《朱熹的政治思想》)②三篇文章,其研究细化之功深得陈荣捷的赞赏③。
余英时和田浩的史学研究方法不同于陈荣捷和谢康伦的就朱子论朱子的进路,他们师徒二人更倾向于走一种更纯粹的史学研究路数,即把朱子思想放在一种综合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为研究朱子思想和道学运动的产生发展过程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在这个大前提下,余英时和田浩的研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余英时师承于钱穆,更关注朱子时代的历史政治背景,而尽量避免对朱子思想和道学运动做纯粹哲学化的抽象讨论。他在自己的朱子学代表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④中用翔实的史证说明,对朱子和同时代的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在逻辑上先于哲学思辨。他指出,道学运动远不是程朱学派一方的宏愿,而是多个道学派别交锋的结果;并且这种道学党争更多是以政见上的分歧——而不是哲学思想上的殊异——为基础的。比如,在探讨朱子继承程颐评论张载的《西铭》时由“民胞物与”概括出的“理一分殊”思想的篇章中,余英时指出,朱子对“理一分殊”的提倡是为了抗衡林栗等人对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政治内涵的质疑。林栗固守君主专制,认为民胞物与暗示的“人人为兄弟”的思想可能引发天下混乱。而朱子则认为,民胞物与、理一分殊表达了士大夫须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与君共治天下这一社会政治理想。⑤
相比之下,田浩更关注朱子时代的思想运动,对朱子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历史事实则相对涉及得少些(当然,田浩对朱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书院教育对形成道学群体的影响,道学运动成员们参与的政治斗争,等等——也有诸多探讨,只是他并不认为这些社会政治环境是左右道学运动进程和朱子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的两部朱子专著——Confucian Discourseand ChuHsi's Ascendancy(《儒家论述与朱熹之执学术牛耳》)①与Zhu Xi'sWorldofThought《朱熹的思维世界》②——中,田浩将考察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考察与朱子同时代的儒者(不仅是朱子门人)以及其他思想家在道学运动和朱子崇高地位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考察道学运动如何由最初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运动发展演变成思想运动,最终使道学在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田浩认为,不论是朱子的崇高地位还是学界所谓道学运动的一致性,都是被后世神话化的表象。田浩将道学运动分为四个思想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道学运动其领导人物各不相同,他们对“我们的道”“纯粹的儒者”“我们的学派”等道学运动中的关键字眼都有不同的理解,而朱子的崇高地位是在第三个阶段(朱子提出“道统”观念并与其他儒学派别发生思想冲突)和第四个阶段(朱子病逝后,其门人尊朱)才确立起来的③。在这个意义上,田浩认为,虽然朱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并不是自道学运动伊始就被尊为道统象征的,毋宁说,他的崇高地位是在与其思想论敌的交锋中逐渐确立的;另外,道学运动的发展史表明,朱子的道学派别所抱持的政治信念和文化诉求是在与哲学思考的互动中逐渐确立其权威性的④。
如果说北美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用于探究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实践活动背景,那么日本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着力的方面则相对更为广阔。除了像吾妻重二的《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史的地平》①运用史学方法分析魏晋玄学和佛道思想与朱子思想的相互影响并考察朱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之外,日本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还用于考察朱子思想的形成脉络。其中比较经典的作品有田中谦二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②、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研究》③、市来津由彦的《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④、明德出版社的《朱子学大系》⑤等。以下简单介绍一下这几部作品的内容。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的成书灵感源于田中谦二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的朱子学共同研究班⑥。这两期研究班的成员们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作为中国古典戏曲专家的田中由此对朱子学产生了兴趣。他注意到,由于《朱子语类》是朱子的不同门人对朱子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那么,如果明确了这些门人师事于朱子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朱子思想的形成和变迁的原始轨迹。田中反复比勘《语类》中的双行小注和两名以上弟子同席记录之处,同时参考《朱子文集》及其他宋人的文集,最终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出版了至今仍被国际汉学界奉为朱子学研究经典之作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佐野公治的《四書学史研究》考察的是朱子创立四书学及宋明学人对四书学的发展,是四书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市来津由彦的《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朱熹思想形成的“场”——北宋末南宋初的闽北程学》——论述二程之学于两宋初期在福建的发展。第二部分——《朱熹门人、交游者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是全书的重点,考察了朱子交友、讲学、传道授业的过程。市来用小传和图表整理了朱子毕生的交游者及门人的资料,分析了朱子讲学的实态及其影响,并对朱子与何镐、廖德明等学者的交往讲学经历做了深入调查①。
相比于田中、佐野、市来等学者对朱子思想在特定时段内的形成脉络的专注,日本朱子学界的另一大部头作品《朱子学大系》的视野则更为开阔。这套由八十余位学者共同执笔的全十四册丛书涉及朱子学形成的思想背景(第一至第三卷)、朱子的主要论著(第四至第九卷)、朱子学在明清时期的展开(第十、第十一卷)以及朱子学在朝鲜与日本的研究概况和发展历程(第十二至第十四卷)。同时,这套丛书还收录了钱穆、唐君毅、秦家懿、陈荣捷等许多海外知名学者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和通论性文章,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三 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虽不似考证学研究和史学研究那般忠于朱子思想原典,却仍然是立足于原典,进而做一些义理阐发。在传统意义上,这种阐发表现为基于道统意识发明朱子思想的元素。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学术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朱子学在欧美的崛起,朱子学的义理阐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哲学思想研究的形态,表现为将朱子思想对象化并予以客观考察,其基本形态是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当然,传统的义理方法也并未因此消亡,而是有了新的目标,即坚持以朱释朱,尽量避免西方语词对朱子学的渗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传统研究式的和哲学研究式的——在当代的各个海外朱子学研究地区(日本和欧美)都不乏传承者,也就是说,20世纪前在义理分析方法上偏于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界在当代吸纳了欧美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而当代的欧美朱子学界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传统的义理分析方法。这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海外朱子学界在运用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上取得的卓著成果。可以说,义理分析方法是当代海外朱子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①。
义理分析方法在日本朱子学中的影响力是与东京大学学派(以下简称“东京学派”)的贡献分不开的。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长期执教于东京大学的已故汉学专家宇野哲人及其弟子后藤俊瑞、友枝龙太郎等。在1990年以前,该学派与九州大学的体认派并称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流派。东京学派不但于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研究上建树颇多②,而且是用义理分析方法研究朱子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学派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的主要朱子学著作有:宇野哲人的《儒学史》③及其续篇《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④,后藤俊瑞的朱子哲学系列论著⑤,山根三芳的《朱子伦理思想研究》⑥,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⑦,大滨皓原的《朱子的哲学》⑧,等等。
宇野哲人在《儒学史》和《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围绕“宇宙论”“心理学说”“伦理学说”和“名分论”四个范畴展开了对朱子哲学的考察,并将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一书中,分三部分——“规范论”“德论”“实践论”——探讨了朱子的伦理思想,主要考察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成及其在朱子文本中的意义和现代意义。后藤的弟子山根三芳在《朱子伦理思想研究》中延续了后藤的思路,从道德意志论和朱子的“敬”“天”“共生伦理”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朱子伦理学。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讨论了朱子思想中的意识、存在、知识与实践等问题,分析了朱子知识论体系里“格物”与“反省知”“悟觉知”的关系以及朱子的格物说与他的政治实践的联系,并另辟蹊径地从朱子和陆九渊的不同生活背景为朱陆学说的差异寻找根本原因。大滨晧原的《朱子的哲学》颇有创见地提出了“理气合离”的思维方式,为化解朱子理气说中的诸多矛盾提供了依据①。
当然,除了东京学派的学者之外,日本的朱子学中运用义理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其中,走传统义理分析路数的名作如垣内景子的《「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②。垣内是日本为将《朱子语类》翻译为现代日语版本而专门成立的译注出版中心的骨干成员,也是当代朱子学中主张朱子哲学为广义“心学”③的代表人物。她的这本著作分为“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和“作为理学的朱熹思想”两个部分,考察了朱子的“心”“敬”“理”等主要概念,特别强调了朱子思想中的“心”层面,是作为广义心学的朱子学的代表作④。而采取哲学式义理方法的研究名作也有不少,如,安田二郎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⑤、汤浅幸孙的《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⑥、木下铁矢的《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①,等等。
《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收录了安田二郎四篇关于朱子的论文。安田在将朱子学文献烂熟于心②的基础上,将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于他的朱子学分析中。在其中一篇讨论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题的论文中,安田用法国哲学家Félix Ravaisson的习惯论分析朱子《论语集注·学而篇》的首章,指出朱子对“学而时习之”的解释与格物说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论及习惯在打通道心与人心、弥合“理”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的两面性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本书另一篇讨论朱子理气说的文章中,安田把朱子的理解析为“意义”,而把朱子的气描述成一种瓦斯状的气体。安田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日本学界饱受争议,但由于他的结论是基于对朱子文献的梳理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所以他的这本书至今在日本朱子学研究领域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中,精通德国哲学的汤浅幸孙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存心伦理” (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 (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考察中国伦理思想,并将朱子的伦理思想归于“存心伦理”。木下铁矢的《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则从西方哲学的理论角度对朱子的时间观、道论、易学、理学等思想给出了独特的解读③。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个误解。大陆学界多以为日本朱子学偏重于文献(主要体现在考证研究和史学研究)而缺乏对义理诠释的关注。经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日本朱子学对文献的重视是基于文献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的“第一序”的意义,即任何脱离文献解读的义理阐发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日本朱子学也并未因重视文献而忽视义理,相反,如我们从东京学派以及垣内景子等学者的论著中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日本朱子学者的著作中,文献和义理是互为支撑的,文本解读中蕴含了某种解释理论或义理分析,而义理分析也多从解读文本处着手。
北美方面,陈荣捷的《朱学论集》①和伽德纳(Daniel Gardner)的两本论朱熹解经的著作是运用传统义理分析方法的名作,但这两位学者的传统义理方法又各有特色。而孟旦(Donald Munro)则是运用哲学式义理研究方法的代表学者。
陈荣捷的《朱学论集》②延续了我们在之前介绍的他用史学研究方法写就的三本著作的理念,即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他对程朱之异的讨论、对朱子近思录的考察、对朱子仁说之来源的考证及其与张栻仁说的比较等,都是他填补以前朱子学研究空白的创见之作,虽然这本论文集不乏他用史学方法研究朱子的痕迹,如,对朱陆鹅湖之会的补述、对早期明代程朱学派的考察等,但这本书的亮点更多在于他从哲学义理方面对朱子学的研究,陈荣捷可谓“以朱释朱”的典型,他的义理分析“不用西洋名词或概念,不愿以洋冠洋服加诸朱子”③。但他同时强调本文集的意图“为申述朱子。不在宣传,亦不事辩护”④,所以又与旨在接续道统的体认式研究方法略有不同。
与陈荣捷“以朱释朱”的进路不同的是,孟旦试图把他对朱子的解读置于人性论、道德心理学等当代哲学问题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试图实现朱子思想与当代相关哲学问题的结合。1988年出版的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⑤是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论朱子的著作。孟旦在其中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朱子的人性观及其政治内涵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分析。他首先将朱子的人性观重构为四对“结构性的形象”(structural images)——家庭与流水、明镜与身体、植物与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花大篇幅分析这四对形象的意义。继而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朱子的人性观中可能蕴含的一种张力,即模仿模范的倾向(可能导向极权主义)和自我发现的倾向(可能导向平等主义)之间的张力①。由此,孟旦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见(我们可以将孟旦的这个结论与狄百瑞的朱子“心学”主张做一个对比):朱子并不相信个体之“心”有得“道”的可能,所以朱子所强调的“立志”并不具有西方“自由意志”的内涵——这可能恰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哲学根源②。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A Chinese EthicsfortheNewCentury(《新世纪的一种中国伦理学》)③中,孟旦延续了他对儒家人性论的关注,只是他转变了之前的哲学人类学视角,转而将儒家人性论与进化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的当代理论相结合,再一次对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伦理学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自然主义的解读。
伽德纳在朱子学的义理研究方面自成一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所取的似乎是广义的“以朱释朱”的进路,即不似孟旦那般将西方思想观念引入朱子学分析中,而是从注释、理解朱子典籍入手从事义理研究。但他与陈荣捷的“以朱释朱”进路也不尽相同。在陈荣捷那里,对朱子学的义理分析虽以对朱子文本的校勘注释为根据,但并不止于校勘注释。而在伽德纳这里,校勘注释(特别是对朱子解经之作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一种义理分析。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体现在伽德纳的以下两部著作中:ChuHsiand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onthe Confucian Canon(《朱熹与大学:宋儒对儒家经典的反思》)④,ZhuXi'sReadingofthe Ana-lects:Canon,Commentary,and the ClassicalTradition( 《朱熹的 〈论语〉解读:经典、注释、经典传统》)⑤。我们知道,伽达默尔(H.G.Gadamer)诠释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是,任何诠释都不可避免地与哲学上的前理解相关联。伽德纳的以上两部著作就是这个主张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详细注释朱子对《大学》和《论语》的解经著作,考察了朱子解经的前提,这些前提恰恰就是朱子哲学思想的体现,而伽德纳对这些前提的考察也恰是他对朱子思想进行义理分析的表征。在注释朱子对《大学》的解读时,伽德纳指出了朱子对“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格物”“致知”等的读解如何相异于汉唐古注,从中阐明了朱子在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上的新意。而在注释朱子的《论语集注》时,伽德纳则将朱子的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相比较,以见出朱子作为一名积极阅读者的解经策略(通过解经将自己的哲学观点注入经典中)和传承道统的使命感。通过这些分析,伽德纳让读者看到了注释经典所可能具有的原创力量(这也许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不热衷于构建系统哲学的原因之一),这种力量使解释者与被解释的经典之间——朱子与《大学》和《论语》之间、伽德纳与朱子的《大学集注》和《论语集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互动关系。
欧洲当代朱子学的义理方法以哲学式见长,在内容上主要是探讨朱子的神学观,这可能与耶稣会的“合儒”传教策略①有关,并经由早期耶稣会在华教士关于God与儒学“上帝”“天”之间关系的大讨论②而进一步深化。在当代欧洲对朱子神学观的探讨中,除极少部分学者否认朱子思想中存在人格神概念——如,李约瑟(Joeeph Needham)③通过详细分析朱子思想的科学倾向论证了朱子对永生与神的否定——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子是有神论者,其中对朱子神学观进行系统探讨的著名学者当属布鲁斯(J.Percy Bruce)和福克(Alfred Forke)二人。布鲁斯在他的文章The TheisticImportofthe Sung Philosophy(《宋代哲学的有神论内涵》)①中指出,朱子之理学中的理、天、太极均有宗教意味;在专著ChuHsi andHis Masters(《朱熹与其师》)②中,布鲁斯更是独立一章专论朱子哲学的有神论意义。而在福克的德文专著Geschichte der neueren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③中,探讨朱子的篇幅比探讨其他任何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篇幅都要长得多,而在对朱子思想的探讨中,对朱子的天、帝、鬼神等神学观念的研究又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然,在欧洲当代朱子学对朱子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中也不乏运用传统义理方法的精品之作。比如,之前提到的布鲁斯的专著ChuHsi andHisMasters(《朱熹与其师》)和福克的德文专著Geschichte der neueren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中,均有对朱子性命、心、仁、道等思想的研究。另外,法国人萨金静(Galen Eugène Sargent)亦在对朱子排佛论以及朱子敬义夹持修养工夫的研究上有值得关注的成果问世④。
四 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与哲学式义理分析方法有类似之处,注重引用中国哲学之外的概念和思想(特别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想)对朱子思想进行哲学分析。但与哲学式义理分析方法中引用西方概念为分析朱子思想服务的目的不同的是,文化思想比较的方法着眼点在于比较朱子思想与异质哲学体系中的相关思想,以期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彼此借鉴,开拓出哲学新路。
用比较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进路在北美和欧洲朱子学界比较流行。考虑到欧洲朱子学界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如葛拉夫神父(Olaf Graf)、布鲁斯(J.Percy Bruce)、李约瑟(Joeeph Needham)等——并未有朱子学比较研究的专著问世①,且这些学者的比较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并不具有代表性,所以笔者在本节中以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为例进行讨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英译朱子文献的匮乏,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基本停留在以西方哲学为主、朱子学为辅的阶段。以霍金(WilliamE.Hocking)的文章ChuHis's Theory ofKnowledge(《朱熹的知识论》)②为例。这是20世纪美国学界专事朱子思想研究的首篇论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遗憾的是,霍金教授在此文中大体是在西欧的朱子学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朱子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因而他对朱子思想本身的把握(以及朱子思想与斯宾诺莎、柏格森思想的比较)不尽如人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将朱子思想用作阐述斯宾诺莎和柏格森思想的工具。这种缺憾也体现在之后的朱子学比较研究论文中③。这种情况在陈荣捷诸本朱子学考证英文著作④问世之后,才开始有所改观。
大体而言,当代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方法注重于发掘中西文化之间共有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这种发掘呈现出两种走向。一是发掘朱子思想与西方哲学体系相关思想(以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阿奎那、莱布尼茨、怀特海的思想最为常见)的相通处。这一研究走向比较容易流于为比较而比较,在研究深度上略有欠缺,故而只是散兵游勇式地体现于不同学者零星发表的文章中①。另一种走向是通过探讨朱子思想在西方相关话题的思想争论中所可能发挥的调解作用,从而既为西方哲学的现存困境提供可能出路,又为重新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研究走向在深度和分析的细致程度上都超过了前一种走向,因而成为从事比较研究的北美朱子学者的首选。除了许多知名学者发表的一系列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的论文②之外,白诗朗(John Berthrong)的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Whitehead,Neville,and ChuHsi(《论创造性:怀特海、南乐山与朱熹的比较》)③和秦家懿(Julia Ching)的The Religious Thought ofChuHsi(《朱熹的宗教思想》)④是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专著⑤。
虽然白诗朗不是朱子研究的专家,虽然朱子并不像怀特海(A.N.Whitehead)和南乐山(R.C.Neville)那样对上帝本性之类的神学话题或者上帝与创造性的关系这样的主题有过深入讨论,但白诗朗(1998)还是通过考察怀特海和南乐山在“创造性”(creativity)——特别是创造性与上帝本性的关系——观念上的分歧以及朱子对“道”(及“理”“太极”)的生生不息和“诚”“仁”等观念的阐述,颇有新意地论证了怀特海和朱子在关于创造性的观念上所可能达成的共识①。这为怀特海回应南乐山的质疑提供了契机,并为重新思考和阐述“存在”(beings/Being)、“过程”(process)、“本体论”(ontology)、“宇宙论”(cosmolo-gy)之类的西方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这种视角在客观上也为重新审视朱子学界对朱子哲学(甚至是理学传统)的通见提供了契机。
秦家懿(2000)对北美朱子学比较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该书将朱子的核心思想界定为宗教性的,将朱子的“太极”概念视为一种富有动态的、类似宗教观念中的绝对存在或终极实在的东西,并认为被朱子学界视为核心的“诚”“敬”等概念其实是为直接而无中介地领悟这种终极实在服务的。但同时朱子又通过“理”概念保持着超越向度与内在向度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一种颇为新奇的朱子学诠释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朱子学界对推崇格物致知的朱子冠以“理性主义者”的标签,转而将朱子诠释为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宗教神秘主义者(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朱子的神秘主义是即内在而超越的,而不是单论彼岸世界的)②。其二,该书将朱子的宗教思想与西方的宗教哲学传统相比照,指出朱子的宗教观不同于西方唯物论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唯知论模式(以柏拉图传统和基督教的各种诺斯底派(Gnosticism)为标志),以中道的宗教观规避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弊端③。其三,该书采用的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心理移情”诠释学模式,从而能够在对朱子文本有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重构朱子思想。秦家懿对朱子文本的语意分析极尽细致,并在分析中将朱子思想中关于鬼神、礼仪、人性、教化等的重要观念整合起来,配以对从古到今朱子批判者的考察,这种主观地重构客观朱子学(主要是朱子宗教思想)的进路使得这本书成为英文学界中内容相当丰富的朱子研究参考书。
五 体认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注重对朱子著作做客观的学术研究,相反,它关注的是通过阅读体会使自身心灵融入朱子文字背后的血脉,以道统为己任。这其实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篇》章二五),也是朱子最欣赏的一种治学态度。据《朱子语类》载:“兼是为学须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领,方不作言语说。若无存养,尽说得明,自成两片,亦不济事,况未必说得明乎?”①若没有在自身存养上下工夫,只是耽湎于训诂考据,则是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崇尚体认式研究方法的学者是最得道统真传的。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它独立出来加以讨论。
在日本,以楠本正继及其弟子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佐藤仁等为代表的九州大学一派是以体认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学者以体认(而不仅仅是研究)朱子学为学术特征,所以通常他们得出的结论颇有独到之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于朱子研究学界颇有影响力。遗憾的是,虽然荒木和佐藤仁至今仍活跃在学术一线,但如今的九州大学汉学界已鲜有人继续以体认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了。鼎盛时期的九州学派运用体认研究方法的代表作有②: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③、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④、冈田武彦的《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⑤等。
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享有广泛声誉,是对宋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分为“宋学”和“明学”两部分,其中“宋学”部分论及了朱子,其中多有见解独特之处。如,楠本将朱子思想体系概括为“全体大用”四个字,并将朱子推行社仓法的政治作为与全体大用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政治作为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①。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是儒佛思想相互影响的一个绝佳范例,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架构展开,其间不乏妙思。如,在比较朱子与南宋著名禅师大慧宗杲在思想上的异同时,荒木敏锐地注意到了朱子“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思想中蕴含的关于日常性的思考,认为这种思考比大慧宗杲标榜的证悟主义更有实践性,可以规避禅修体验中超乎人情、世情而可能造成的弊害②。此书虽涉及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但这种比较中贯穿着九州学派辩护朱子的精神,所以笔者仍将之归入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之列。冈田武彦虽然是阳明学的倡导者,却难能可贵地对朱子学有诸多同情的了解。他于《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中发表了五篇专论朱子的论文。这些研究为冈田运用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出版论著《作为活学的朱子学》③)、探究儒学的经世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学者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是实践儒家为己之学的代表人之一。从Neo-Confucian Orthodoxyand theLearning oftheMind-and-Heart(《宋儒正统与心学》)④中通过考察朱子的道统理念来强调个体的“自任于道”,到TheLiberal TraditioninChina(《中国的自由传统》)⑤中将儒家提倡的自主人格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做一衔接的努力,再到Learningfor One's Self(《为己之学》)⑥中对“己”和“道”关系的探索,以及The TroublewithConfucianism(《儒家的困境》)⑦中对儒家人格和君子之道的讨论,狄百瑞念兹在兹的是儒家道统的普世价值和个体传承道统的可能性。撇开狄百瑞通过宋儒的精神风貌探求儒家普世价值的进路是否可行的问题①不谈,单就狄百瑞对宋儒精神风貌特别是对朱子在界定道学正统上的重要作用的考察来说,狄百瑞的研究还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朱子强调个体内省之“心”如何“居敬”以使先知(prophet-ic)启示之“道”化育于自我,并由此把“道学”视为“心学”,突出了朱子“道学”中的宗教意味②。
六 其他方法
(一)索引的方法。
应该说,当代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是与对朱子文献的索引编纂工作分不开的。朱子学中的索引方法指的是从朱子著作中摘出重要术语,著录成按一定检索顺序排列的简明条目,并注明该条目在原著中的页码,以方便研究者搜集、查找和研究朱子原始文献。这方面的研究属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后藤俊瑞编纂的“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包括了《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与《诗集传事类索引》③三种)、佐藤仁编纂的一系列索引(《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④、为《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⑤中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编制的人名索引以及为《中日合璧版朱子语类大全》⑥编制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以及东京大学朱子研究会的二十余位成员经过十七年辛苦努力编纂而成的大型索引《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⑦都是其中的精品。
(二)疑古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本应属于广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但由于这种方法并不以还原朱子思想的实态为旨归,而是以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批判朱子思想,检视朱子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所以笔者将这种方法从史学研究方法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考察。
自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津田左右吉开创这种研究方法以来,当代日本的朱子学界乃至宋明思想研究界不乏这种思想的追随者。津田本人受中国清代学者崔述的“疑古辨伪”思想和德国史学家Leopold VonRanke创立的兰克史学派的双重影响,以疑古和史料批判为纲,以质疑、批判中国和日本古典文献记载内容真实性为己任。与其师白鸟库吉从事满蒙地理研究和西域研究不同,津田对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史颇感兴趣,并将疑古批判式的方法带入了他的中国思想研究中。虽然津田本人并未将疑古批判的方法专门用于朱子研究,但土田健次郎和小岛毅等学者则将这种方法延伸到了朱子学研究领域。土田健次郎在《周程授受再考》①中,否认朱子关于二程师承于周敦颐的说法,主张二程是道学的实际创造者。而小岛毅则为土田的书所写的书评《“周敦颐神话”的崩壊》②中,全然支持土田的立场,甚至不无戏谑地对朱子的学术人格提出质疑。虽然有日本学者对这种过分轻视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异议③,但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青睐的大有人在,更有学者以此为契机,指出当代日本宋明思想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脱离神话主义”④。
应该承认,这种疑古批判式的研究方法的确有其自身优势。相比于某些“崇朱”的研究方法,疑古批判的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突破朱子设定的视野,回归历史真相,凸显研究者自身的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潜在的危险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危险性远大于疑古批判具有的研究优势。过分地强调对朱子视野的突破可能导致在未深入朱子语境的情况下妄下论断,乃至揶揄前人、失之轻妄而不自知,这既是严谨治学的大忌,又偏离了疑古批判研究方法的本意。
(三)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着眼于在现实中运用朱子著作所蕴含的道理,以求为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哲学诠释学主张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①过程充分表明,通经致用是经典诠释(主要是义理分析方法)的题中之意。笔者在本文中将通经致用的方法独立出来,是为了强调这种研究方法在追求用世的前提下所可能导向的治学大忌,即得鱼忘笙地主张对经典做超出其文本范限的解读。在今日学界日益盛行的用世风潮中,保持对上述治学禁忌的警醒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而海外朱子学界运用通经致用方法的名作无疑为我们学人保持这种警醒提供了极好的范例。除了之前讨论诸种诠释经典方法时提到的相关著作(如孟旦的论著)外,冈田武彦的《作为活学的朱子学》②和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③的第三篇(“实践论”)中对“恕”概念的现代意义的探讨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四)意识形态式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指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术语和思想用在朱子学研究中,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颇为盛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之一④,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力量真正成型却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至70年代①。受此影响,这段时期内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也出现了用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分析朱子思想这一分支。代表著作有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②以及守本顺一郎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1967)③。岛田虔次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把朱子和阳明思想放在同一个思想史脉络中进行描述,并分别冠以“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称谓。而守本顺一郎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随处可见“丸山政治学”④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丸山将朱子学定位为封建思维在中国的完成形态及其对朱子的生产论的阐述等都可以被解读为守本朱子学研究采纳上述两大思潮思考模式的结果。
以上,我们通过对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主要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予以分析、提炼,总结出了考证、史学、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体认式等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并非截然相分,它们彼此间有交集。比如,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之间就有可能重合之处,这是因为,研究者在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朱子思想的哲学阐释时有可能需要借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和思想,从而涉及运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再如,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与考证的方法、史学的研究方法、哲学义理式的研究方法、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等之间亦有交集。因为体认式的研究可能以考证、史学研究、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等方式呈现出来,也可能以通经致用为最终诉求。另外,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方法也可能是相互结合的。比如,信广来(ShunKwong-loi)就主张一种由考证而义理的方法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方法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节 韩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②
一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传入朝鲜,经过高丽王朝时期100多年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到14世纪末成为朝鲜李朝的建国理念(即官方哲学),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对此后500余年间朝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期,为朱子学的初传阶段。嘉定十七年(1224)春,朱熹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等到达高丽全罗道的锦城,建立书院讲学,传播朱熹思想,这是朱子学在朝鲜民间传播之滥觞。而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引起统治者重视的则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安垧、白颐正等人。安珦(1243—1306)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朱子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教之正脉,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横经受业者动以百计”。③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④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1298年随忠宣王到元大都燕京,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大量程朱理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珠(颐正)。”①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颇有建树。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
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之所以会在此时传入朝鲜,一方面与高丽同元朝的密切关系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有关。可以说,正是朱子学北传并在元朝取得统治地位,加之高丽同元朝频繁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为朱子学流入高丽疏通了渠道,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程朱理学在中国产生时,汲取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适应了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也为其移植朝鲜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二是14世纪下半期,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阶段。安珦、白颐正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更多地还只是停留在对程朱理学著作的介绍和引进上,还来不及对程朱理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挥,而且传播的规模尚局限于高丽上层极狭小的范围内。进入14世纪下半期,由于朱子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李朝开国后朱子学正式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推动朱子学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
李穑(1328—1396)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李齐贤(1287—1367)是权溥的女婿,曾跟随忠宣王滞留元大都30年,其学注重程朱的“敬以直内”,反对佛教和汉唐经学。李穑年轻时,曾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学者皆仰慕。掌国文翰数十年,屡见称中国”。③官至宰相。他在成均馆任大司成期间,以朱子学为教育内容并对《小学》作谚解,进行普及,任宰相期间,笃力推行儒学教育,在中央建五部学堂,地方设乡校。史载:恭愍王十六年(1367)“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威,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土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月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尘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①后来对朱子学有创见发挥的学者如郑道传、极近等,多出自李穑门下。
郑梦周(1337—1392)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②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③他对朱子学的阐发,同代人颇为折服。“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④李穑曾高度评价郑梦周:“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⑤
郑道传(1337?—1398)号三峰,他不仅是高丽两班改革派的干城,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他“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鸣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邪说,明天理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⑥权近(1352—1409)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受到郑道传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论。权近的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五经浅见录》是继承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李朝时期刊行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溯其发端盖出于权近的《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更是远及日本。
这一时期的高丽朱子学,正是经过李穑、郑梦周、郑道传及权近等的大力推动,加之它适应了当时改朝换代的社会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新王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李朝(1392—1910)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1392年李朝开国。李朝统治者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李朝开国到1876年日本势力入侵朝鲜的近500年间,朱子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甚至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也只有借助朱子学的外衣才能存在。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为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到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退溪学的代表人物李滉(1501—1570),字景浩,号退溪,是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退溪集》(68卷)、《朱子书节要》、《启蒙传疑》、《心经释象》、《天贫图说》、《四端七情论》等。李退溪终身尊信朱熹的思想和学问,武夷山是朱熹晚年弃官隐居和沈潜学问的地方、陶山是李退溪隐居的地方,自古以来又叫作武夷。1183年4月,朱熹54岁时,在武夷山建盖了精舍,翌年写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因物寄兴,沿着武夷山的九曲描写了名胜和景物特色。退溪阅读了《武夷山志》之后,从想象中游览了朱熹隐居的武夷九曲,继承了朱熹《武夷棹歌》的形式,写了《次武夷棹歌》十首,引端了后来韩国各地指称九曲的潮流。如18世纪后期李野淳等人进行的陶山九曲的设定和有关诗歌的创作,他的《陶山九曲》诗次韵朱熹的《武夷棹歌》,又把李退溪的《次武夷棹歌韵》的意向当基础,描写了陶山一带的山水风光。退溪的《武夷棹歌》和韵不仅形成了韩国诗歌史的传统脉络,而且退溪学派的人往往把陶山九曲看成想象武夷和学习朱子的体验空间。①在哲学上,李退溪直宗朱熹,持“理一元论”观点,主张理贵气贱说和理气互发说,重视实践意义的“敬”,强调世界万物产生于“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动静乎”。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先知后行”,强调“性”有纯善无恶的“本然之性”和善恶不定的“气质之性”之区别,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启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之先河。其所创建的陶山书院,至今仍是韩国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书院。退溪学目前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由首尔退溪研究院创办于1973年的《退溪学报》,至今已经发行了一百多期。由退溪学釜山研究院创办的《退溪学论丛》至今也已发行了十余辑。退溪学国际会议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以上。韩国首尔和釜山、日本东京和福冈、中国北京以及香港和台北等城市都曾主办过研讨会。退溪性理学、退溪诗学等相关专题的研究始终都是学界的热点。
这一时期朝鲜朱子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李珥。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世称栗谷先生。1558年去陶山拜李混为师。1564年考中生员、进士科和明经科,历任户曹佐郎、吏曹佐郎、户曹判书、大提学等官职。在因病辞官期间,他回到地方专心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著有《栗谷全书》44卷。李珥反对“理气互发论”,主张“理气兼发论”,创立了朝鲜朱子学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他认为世界是由“气”和“理”所构成,“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理气“浑沦无间”,“实无先后之可言”,同为世界万物之源。但他又认为如论理气先后之分。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官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反对李滉在“性”“情”上的“四七说”,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认为七情以外无四端。李滉、李珥的“四七论争”,开拓了朝鲜朱子学的新领域,后与李滉一起并称为朝鲜思想界的“双璧”“二大儒”。
以李滉为中心的岭南学派(主理派)和以李珥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气派)的论辩持续了长达三百年之久,而这也是朝鲜朱子学的成熟期和巅峰期。到了16世纪末,朱子学逐渐从学术论辩转到与理论研究无关的“礼论”等问题,甚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党争工具。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畿湖学派分化为“老论”和“少论”。“老论”学者将朱子学化为绝对理念,并以自己的理论为朱子学正统。“少论”学者则反对朱子学绝对化甚至批判朱子学,还出现了郑齐斗(霞谷,1649—1736)这样的朝鲜阳明学大家。与此同时,岭南学派中则出现了“实学”之风,从“利用厚生”的观点来批判观念化的朱子学,谋求儒学的新方向。如以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的“实事求是学派”,主张在研究经典时依确实的考证,理解文本真正的意义;以李翼(星湖,1681—1763)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关心土地制度和行政改革)和以朴趾源(1737—1805)为中心的“北学派”(振兴农业、主张工商业的流通和生产技术革新)则主张理论研究要对现实社会的文物制度和社会文化政策有贡献。实学派观点的集大成者是丁若镛(茶山,1762—1836)。他主张土地和社会制度改革,重视科技,这既使朝鲜从性理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也间接加速了朱子学在朝鲜的衰落。
二 当代韩国的朱子学的研究
(一)20世纪初的朝鲜朱子学。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面对西学的渗入,朝鲜朱子学内部分化为传统论派、开化论派和调和派。三派的思想特点及其研究方法大致如下。
传统论派开展卫正斥邪运动,有原教旨主义的特点,大都奉行尊华攘夷的义理思想,秉持朱子“理尊气卑”的形上学,视儒学为理、为王道,西学为气、为霸权主义。按照朝鲜朱子学思想体系的两大派——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①——来划分,岭南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震相(号寒州,1818—1885)、张福枢(1815—1900),畿湖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柳麟锡、田愚(号艮斎,1841—1922)、朴世和(1834—1910)等②。由于我们的关注点是当代朱子学,这里将略去对几位19世纪的传统论者思想的考察,而关注柳麟锡、田愚这两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论者的思想。
柳麟锡主张,儒者在国家变乱之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态度:第一,发起义兵以扫清逆党;第二,即使离开国土,也要守住旧制度;第三,奉献生命以遂成其志。③他的理论依据是理尊气卑、理主气客的思想。他指出,“其所本者理,所形者气,而理气元是帅役上下”①。但他的兴趣点并不在讨论理气的关系,而在于以此为依据,强调民族自主和确立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批判当时朝鲜的西化倾向。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五伦”乃是据于天理,而西方的新教育则只是追求形气以满足欲望,因此是应当拒斥的。另外,西方新教育的推行是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之一,所谓的西化不过是日本希望引导朝鲜脱离清室、逐步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实现韩日合并的奸邪诱饵。
类似地,田愚的研究也是将性理学作为理论基础,而着眼于解决当时韩末的社会危机。不过,他的性理学主张与柳麟锡的有冲突。在《两家心性尊卑说》(1918)一书中,田愚指出了他的性理学主张与其他学派的主张的不同:他主张“性理心气论”,认为心是气而不是理,因为心并非静而无为,而是动而有为的;相比之下,其他学派则主张心主理,而没有看到心须依理合理才能无偏失的道理。在此基础上,田愚在《从重时中辨》(1905)一文中指出,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体现“性即理”说,而夷狄和异端则只能随“心即气”的欲望思考和行为②。与此相呼应,田愚在《与郑君祚》(1877)③、《论裴说书示诸君》(1908)④等一系列书信中提出,应对当时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当权者作性理学的内圣修养,并施行排斥夷狄之开化论的政策。随着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加剧,田愚选择了隐遁守旧而力保华脉,将余生奉献给了朱子学乃至中华文化的教育和写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论派主要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即他们对朱子思想和著作的讨论是以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为旨归的。
再来看开化论派。秉持开化论的学者们⑤积极接受西方新学(主要是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进化论),批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的无用性,提倡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甚至将被日本殖民的亡国原因归咎于儒学,以为朱子学空谈心性,阻碍智力发展,并以腐朽思想求生存,实乃缘木求鱼①。
最后来看调和派。调和派由一些活跃于政界的儒者组成,提倡以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体新用论或儒体西用论,反驳开化论对儒学的批判,认为开化不是无条件地仿效西方,而是要适合自己社会的现况。这一派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如朴殷植、金允植,等等)是韩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②。调和派鲜有朱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是持批判朱子学的立场的。其中,朴殷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朴殷植在早年(1859—1897)属于传统论派,仅以朱子学为正学。在经历了甲申政变(1884)、清日战争、甲午更张(1894)等事件之后,朴殷植看到了传统论派在对抗日本侵略上的无力性,遂转而批判朱子学。他一方面创立“大同教”(1909),作为儒家改革的主体;另一方面,推广阳明学,批判朱子学。在《儒教求新论》(1909)一文中,朴殷植指出了朱子学的三大弊病:第一,朱子学只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工具,与儒家的根本政治思想(民本主义和大同主义)相背离;第二,朱子学只是消极布教的权威主义而已,偏离了孔子周游列国思以易天下的理念;第三,就学问本身来说,朱子学支离繁杂,所讲的“知”与新学的科学之知是同一知识层次;而阳明学的良知则高于科学知识,可以吸收各种科学,纳于良知之学内。③类似于传统论派,朴殷植也同样运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只是他的通经致用方法是从批判朱子学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朱子思想,比如,将朱子学在现实运用中的教条化归咎于朱子思想本身,并将朱子的“知”等同于闻见之知。
(二)1905—1945年的朝鲜朱子学。
1905—1945年期间,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朱子学作为朝鲜本国文化传统的代表而遭到了歪曲①甚至废止,这令20世纪初传统论派的复兴朱子学努力严重受挫。朱子学乃至儒家文化都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处于低谷期。尽管如此,一些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却仍致力于延续朱子学和儒学的命脉。这段时期内比较著名的朱子学和儒学成果有: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何谦镇的《朱子書節要》(1939)、《东儒学案》(1943)。
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是韩国首部近代儒教通史。张志渊曾任《时事丛报》《皇城新闻》的主笔,并在满洲条约签定时,发表社论《是日也放声大哭》(1905),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在《朝鲜儒教渊源》一书中,他受到韩国实学的影响,将奉行朱子学抽象理论的性理学家斥为小人儒,与他所推崇的李翼(星湖)、丁若镛(茶山)等君子儒区分开来,认为朝鲜李朝衰亡原因是因未用君子儒或真儒。他既批评传统论派不知变通、拘泥于性理和训诂,又批评开化论派不懂得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盲从西学之浅表,认为二者均失其中,主张儒教伦理与近代科学可以参互变通。他表示,西方的科技是近三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故论古代文明,则东方优于西方,只是旧儒们拘泥固执,而使儒学浮虚无灵,才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衰落。
何谦镇(1870—1946)堪称以道统为己任的典范。他本人曾以儒者身份参与独立运动,并两次入狱,并于1931年创立“德谷学堂”,晚年著书立说,致力培养后学。他的《东儒学案》(1943)可以算作朝鲜儒学史上唯一的学案。朝鲜儒学史上类似的著作是朴世采的《东儒师友录》(1682)和宋秉瑄的《浿东渊源录》(1882),但在影响力上皆不及《东儒学案》。《东儒师友录》包括了薛聪以下的750位学者,但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他们的师友渊源和行迹的,而不是关于思想。另外,这些被选择的人物大都是畿湖学派的学者,时代也局限于18世纪后期。《浿东渊源录》参照了朱子《伊洛渊源录》的体例,兼参《东儒师友录》,主要记述人物的思想渊源,多引用关于人物行迹的材料,而不是人物的思想观点,且未区分学派。相比之下,《东儒学案》则要全面很多。《东儒学案》分为上、中、下三册二十三篇,每个学案里,都包括学派来源、代表学者的生平和学问特性、思想特色等内容。何谦镇以道统论的观点成书,认为理学为儒学正统,并以朱子学为理学正统,以退溪学派为中心。尽管本书重视道学义理实践、而不注重性理学的哲学理论和各学派的学问异同,从而未论及朝鲜阳明学派(江华学派),但是全书对各个理学学派的分殊和脉络均有细致而公允的分析和评价,这使得此书的分类构图一直为人所称道,也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不失为研究韩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一项重要参考文献。
(三)20世纪40—70年代初的朝鲜朱子学。
1945年之后,朱子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处于低谷期。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在经历了促进韩国近代化进程的甲午更张运动以及日本实行的彻底抹杀韩国传统文化的政策之后,中断的文化传统已很难迅速复苏。第二,光复之后的韩国处于文化过渡期,而朱子学没能通过自我改革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力与其他各类文化竞争,当然也不能主导韩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三,美国军政时期(1945—1948),西方文化渗入,致使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很难一枝独秀,韩国民众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很难对朱子学有亲近感,加之韩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逐渐西化,仅有极少数韩国大学维持朱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命脉。第四,韩国政府和民众都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富裕上,进一步造成了传统伦理价值的危机。第五,在经历朝鲜李朝崩坏、日本殖民统治之后,20世纪的韩国基本上每十年有一动荡,50年代南北对峙、60年代学生民主革命和军事政变、70年代实施巩固维新独裁体制,韩国社会处于长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中,这对于20世纪初就岌岌可危的韩国朱子学来说,无疑又是新的挑战。特别是50年代的南北对峙以及60年代实学思想的复兴(克服朝鲜朱子学空谈心性的倾向,力求回到原始儒学的质朴面貌,兴起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都是对朱子学研究的阻碍。
1945年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论著有:玄相允《朝鲜儒教史》(1949);李丙焘《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1959)以及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郑寅普、李相殷的著作。
玄相允的《朝鲜儒教史》采用文本考据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朝鲜朱子学两大富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对峙为主线,勾画出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脉络。李丙焘的《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则采用了史学研究方法,考察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朝鲜的发展轨迹,着重于梳理这两派在朝鲜的历史流变,而不是进行思想分析和论述。
郑寅普和李相殷的著作可以被看作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两大思想体系——阳明学现代新儒学和朱子学现代新儒学——之间的争论的绝佳范本。同为韩国现代新儒家,两大思想体系皆主张兼采东西学术之长,综合新旧之学,但对何为东方学术之长的问题有争议。郑寅普著有《阳明学演论》①,继承了20世纪初的朝鲜阳明学家朴殷植的批朱立场,认为阳明学与朝鲜民族意识能自然结合,圣贤之道在于人心未亡,而其人情自身则是至善良知的表现;而朝鲜儒学流弊则生于朱子学,朱子学或讲论心性而少于己身的良心契合,或标榜道义却以此图谋私利②。李相殷则是朱子学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他著有《〈大学〉〈中庸〉之现代的意义》《再论东洋文化》《从humanism看儒教思想》《批判国史教科书之性理学叙述》《儒学与韩国思想》③《四七论辩及对说、因说的意义》④等,旨在匡正对朱子学的流俗偏见,并试图熔铸朱子学与现代学问。类似郑寅普,他也提倡修正儒学重义轻利、内本外末的思想,主张兼顾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但他认为朱子学的性理之学并不像阳明学者理解的那样与现实生活相疏远,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的,从而实学并不与性理之学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无实学之性理学为空虚,无性理学之实学为盲目也。”⑤具体说来,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当今价值在于三方面,其一,看到制度的制定和改革并非万能,制度操作者的道德性更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教义是基础;其二,西方的历史呈现出对立分裂形态,而儒家则提示出一条合作、统一之道,比如,秦、汉统一就与儒家的政治哲学经典《大学》和心性哲学经典《中庸》的出现关系密切;其三,肯定朱子对《大学》的格物释义,认为其具有科学精神,可以视为清代实学和韩国实学的鼻祖,朱子学较之陆王学,具有更踏实的学风和现代意义。
(四)多元化时期的朝鲜朱子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韩国社会的国际化,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开始流行,其中不乏正视传统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在各个大学重视复兴传统文化、增加研究人员以深化学术研究的风潮推动下,为朱子学的复兴带来了新的生机。韩国学界甚至兴起了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并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韩国学者梁承武(2008)的统计,从80年代开始,有关朱子学方面的单行本、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等各类论著较80年代前有了极大增长,而研究广度也极大提升①。就广度来说,这些研究涉及了朱子及朝鲜历代朱子学大家的哲学思想(以理气论、工夫论等方面的研究业绩较为丰厚)、散文和诗歌研究、教育思想,等等。然而,从研究的深度来说,70年代之后的朱子学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大多数研究都缺乏思想上的创新意识,而以客观、逻辑性的思想史研究或文本研究为基本特征,即只停留在研究朱子和历代朱子学大家的思想、论著和言行的层面,把儒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从70年代至今,涉及韩国朱子学史研究的论著及论文主要有:裴宗镐《韩国儒学史》(1974)②、《韩国儒学资料集成》(1980),李东俊《关于17世纪韩国性理学派历史认识的研究》(1975)③,韩永愚《朝鲜前期性理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1976)④,柳承国《韩国的儒教》(1976)、《东洋哲学研究》(1983)⑤、《韩国儒学史》(1989)⑥,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1980)⑦、The Korean Controversy over ChuHsi's ViewontheNatureofMan and Things(《韩国学界关于朱熹论人、物之性的争论》,1982)①、《东洋思想与韩国思想》(1984)②、《退溪李滉的哲学思想》(2000)③,权延雄《世宗朝的经筵和儒学》(1982)④,李楠永《理气四七论辩与人物性同异论》(1984)⑤,琴章泰、高广稷《儒学近百年》(1984)⑥,金忠烈《高丽儒学史》(1984)⑦、《韩国儒学史》(1998),李成茂《朱子学对十四、十五世纪韩国教育及科举制度的影响》(1986)⑧,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 (1986)⑨、 《韩國儒学史》 (1987),玄相允《韩国儒学史》(1986)⑩,崔英辰的五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史》(1997),姜在彦《韩国儒学两千年》(2003),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室编的七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大系》(2005—2007),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2008)⑪,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2011)⑫,等等。其中也不乏研究韩国大儒的思想的论著,如韩永愚《郑道传思想研究》(1983)⑬,李东翰《技术之危机与敬哲学之解答》 (1988),申龟铉《西山真德秀之〈心经〉与退溪李滉之心学》(1988),李基东《李退溪的人道主义和敬》(1988),丁淳睦的《朱晦庵和李退溪之书院教育论》(1988)⑭。还有一些是比较韩国儒学与其他国家儒学研究状况的论著,如,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1995)①。
这些论著主要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梳理朱子学在朝鲜的发展脉络(或某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或者横向考量朝鲜朱子学研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朱子学研究之间的异同。比如,裴宗镐(1974)探讨了朝鲜性理学的主要议题——四端与七情论辩及理气论争——的演变过程及论争的焦点所在;柳承国(1976,1989)探讨了朱子学传入高丽的经过以及朝鲜性理学的兴盛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尹丝淳(1980,1984)则以对韩国儒学的特性为分析主线,探讨了韩国神话传说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的权威地位的关系(他认为,韩国神话传说揭露出韩国文化对于超越问题的兴趣,使得性理学家对于朱子学中的“天命”“天人合一”“穷理”等问题有细致的、突破性的讨论)、朝鲜前期和后期思想家对于“实学”和“虚学”的看法的不同(朝鲜前期儒者以佛学为虚学、性理学为实学,后期实学派则以超越训诂和辞章、袖手谈心性的性理学为虚学,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之学为实学),等等。有时,这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以客观叙述为旨归的,而是带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这种研究带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论预设,比如,金忠烈(1984,1998)的儒学史叙述是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儒学并非宗教,不认同来世,而是追求现世的现实主义;而琴章泰(2011)则主张,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并从朝鲜历史上积极实践儒学价值的儒学家的具体功绩研究入手(比如张志渊、何谦镇等儒者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奔走、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等),研究儒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第二,这种研究方法是与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比如,李东翰(1988)、申龟铉(1988)、李基东(1988)、丁淳睦(1988)都是试图通过将研究退溪思想与探讨其现代意义结合起来,为现代社会确立价值目标。不过,从总的研究倾向上来看,大部分采用史学研究方法的论著还是从客观的角度切入的。
除了对韩国朱子学史的研究,70年代之后的韩国朱子学研究也涉及对朱子本人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训诂考据的方法;二是义理研究的方法;三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了训诂考据方法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朱子论著的韩文注译工作。根据梁承武(2008)的考察①,在韩国出版发行的朱子学译著主要有《四书集注》、《小学集注》、《诗集注》②、《朱子家礼》③、《朱子家训》④、《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到卷六“性理三”部分⑤、《近思录》⑥,等等。至今,尚无朱子全套著作的完整韩注本问世,甚至一些朱子的重要著作(如,《四书或问》《仁说》,等等)亦未有韩注本。
运用了义理研究方法的朱子学研究代表作是金永植(Yung SikKim)的一系列朱子学著作。由于他的研究以往较少被讨论到的朱子自然哲学为关注点,发前人之所未发,笔者拟用一定篇幅介绍他的研究内容。
金永植在2000年出版了专著TheNatural Philosophy ofChiHsi(1130—1200)(《朱熹的自然哲学1130—1200》)⑦,研究朱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将朱子的自然哲学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相比较。他首先讨论了朱子自然哲学中的基本概念——理、气、阴阳、五行、象数,等等,并兼论鬼神、天和圣人这些虽“不属于自然世界、但仍与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有关”⑧的事物。接着,他讨论了朱子对自然界的一些论述,比如对物质层面的天地的看法、对万物的看法(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对人的物理、精神、生理各方面的理解。最后,他从与中西方科学传统出发,考察朱子的自然哲学概念和对自然界的论述,比较二者的异同。
金永植在2009年发表的《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①一文中指出,朱子对“自然科学”(天文、历法、医学)和“超自然主题”(如,占卜、风水、内丹、祭祀,等等)均有大量研究,认为它们既是他“格物”学说的体现,又是出仕儒者需要涉猎的课题(因为它们可以增进百姓社稷的福祉)。金永植的文章从以下三方面讨论了朱子对科学和超自然主题的研究:第一,朱子对当时流行的文本做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和注疏,编辑相关著作、确立正确意义、校正错误甚至更动原文,并确立学者应研习的最佳读本。第二,朱子赋予超自然主题以合理性,认为它们并不违背儒家的基本立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气”的概念以及气与心的交互作用为这些超自然主题提供了理据,比如,内丹和风水等技术之所以养生,乃是因为“气”本身的生命特质以及心对人体外阴阳之气的掌控能力,另外,卜筮和祭祀中还涉及人心与天地之气或祖先之气的相互感通。其次,朱子批评同时代的儒者专研《易经》的义理而忽略其占卜面向,指出《易经》卜筮是一种重现宇宙过程的活动,《易经》是联结人体与宇宙运转的主要工具,而占卜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转。第三,朱子对当时超自然的奇异事例时保持开放态度,但将它们归因于气的性质和活动,而不是直接承认有超自然的存在体与力量。金永植还分析了朱子的这种开放态度的产生原因:朱子对智力挑战的兴趣、朱子对自己在许多学科上的卓见自信,以及朱子对古代知识的一贯尊崇。金永植最后总结说,由于朱子对科学与技术的主题给予了足够关注,使得儒学更为完备和开阔,并具有了科学精神;同时,朱子对超自然主题的涉猎,也相对缓和了他的理性主义立场,同时使他的哲学体系更为完备和富有解释力。
梁承武的博士论文《朱子哲学思想之发展及其成就》(1984)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本。该书以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义理内容为中心,讨论了先秦、北宋儒学与朱子思想的师承关系、朱子关于中和问题的论定、朱子关于仁说的论辩、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及理气论以及朱子哲学可能为现代哲学讨论贡献的话题,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该书是当代韩国学界为数不多的对朱子本人的哲学思想予以全面述评的专著,但是从内容上说,这本书却没有太多新的建树,基本上未超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朱子的判教。
(五)小结。
综观之,当代的朝鲜朱子学界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相比于对朱子本人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当代朝鲜朱子学界更重视对朝鲜历史上的朱子学研究大家的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其二,相比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传统社会拥有的绝对影响力和权威地位,当代的朝鲜朱子学乃至儒学已经萎缩,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文化思潮之一。其三,与朱子学的地位变化相伴随,在朝鲜李朝时期成果迭出的对朱子学中的理气心性及人物之性同异等思想的探究和发展,被客观的思想史研究以及为朱子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寻求根基的探讨所替代。
这三个特征在当代朝鲜朱子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有体现。20世纪初,朝鲜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论派和调和论派的学者大都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运用朱子学著作的理论为现实困境找出路。1905—1945年的日本殖民时期,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朝鲜传统文化岌岌可危,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多运用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以道统为己任,使自身心灵融入朝鲜朱子学的血脉,张志渊、何谦镇等朱子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中均有很强的道统意识,致力于延续朝鲜朱子学命脉,且他们本人也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实践传统文化。1945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朱子学的情势虽不及日本殖民时期的灭顶之灾,却仍十分严峻,主要原因之一乃是韩国社会对于朱子学的文化价值产生了质疑。这一情形与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出现的朱子学危机多有类似之处,于是,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也就类似于20世纪初的朱子学研究,即说明朱子学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决定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在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嗣后,复兴传统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朱子学面临的危机逐步缓解,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多样化,但是,韩国社会的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子学权威地位不再的事实,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转而以客观的史学研究和训诂考据研究为主(虽然偶有义理分析的研究著作,却毕竟不是主流),缺乏新的理论建树。
第三节 越南及新加坡的朱子学研究
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时段:19世纪末期,新加坡曾出现过儒学热,甚至被标榜为“儒学复兴运动”①。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在新加坡创办了一系列华文学校(“崇文阁”“萃英书院”“养正书室”,等等),旨在“究洛闽之奥”,并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作为教材②。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儒家伦理教育,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旨在推动儒学在新加坡的复兴。但是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更多的是停留在“通俗儒学”的层面,即作为一种华人道德价值观存在于普通民众中,并以家庭环境熏陶的方式留存。19世纪末的儒学热被五四思潮浇熄,20世纪80年代的儒家伦理教育也仅持续了8年时间,无疾而终(1990年,儒家伦理课程被公民与道德课程取代,东亚哲学研究所也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③。更重要的是,学术层面的儒学研究在新加坡极少专门涉及朱子学,鲜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成果问世。
管见所及,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道运曾经专门从事过朱子学研究。作为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他对朱子学有相当深的研究,著有《朱学论丛》④《日儒林罗山(1583—1657)的朱子学——着重对其教育思想之研究》①《朱熹心学的特质》②等。他主要运用的是以考证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尽心工夫的角度切入朱子理论体系的研究,并兼对元代南北方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的思想以及日儒林罗山的教育思想有深入探究。他指出,朱子的心性践履之学乃是朱子心学的主要特征,体现了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并不相分。朱子由尽心工夫体会心不即是理(因为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与气之上),这是朱子对儒家心学的特殊贡献。类似地,元代的几位朱子学者也遵循了朱子由气质切入切实践履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他还指出,这种朱子式的心学对今日道德修养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提示我们需依本身气质所近而从事切实的德性践履。
相比于新加坡,朱子学在越南的流传是具有相当广度的。秦汉时期,儒学伴随中国移民迁入越南而开始在越南传播(自秦、汉始至五代末,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曾为中国的郡县),越南的儒学已在越南存在了上千年,而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也从南宋末年(13世纪中叶)就已开始③,并在黎朝(1428—1788)到阮朝(1802—1945)的前期达到高峰,成为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在越南思想史上,曾出现了黎文休(1230—1322)、朱文安(1292—1370)、黎贵惇(1726—1784)等从事朱子思想研究的儒者④,并有一系列朱子学研究论著问世①。遗憾的是,朱子学在越南始终没有像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那样得到深化和细化。当代越南从总体上来说,也没有十分突出的朱子学研究成果(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越南的儒学研究成果,毕竟,越南拥有西贡文科大学、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人文与社科大学、汉喃研究院等众多研究机构,以及一大批从事儒学研究的当代学者,如陈廷厚、潘玉、武挑,等等)。管见所及,当代越南尚无朱子学研究专著问世。从越南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先秦儒家及越南儒学发展史上②。
第一节 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本节主要讨论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即20世纪以来该地区的学者对朱子的思想、著作、实践活动等方面加以研究的方法问题。尤以日本和北美这两处朱子学研究重镇为要,同时论及当代欧洲的朱子学。
管见所及,介绍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基本上都关注一阶(first-order)研究的成果,即基本上都以综述当代学者对朱子思想及实践活动的研究状况为目标,而极少涉及二阶(second-order)研究,即基本上不关注当代学者在进行朱子学的一阶研究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问题①。当然,朱子学方法论的这一研究缺憾并不表明方法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对于任何一个理论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发展前景,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方法论问题对于未来朱子学研究(无论海内还是海外)的走向和突破性成果的取得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有鉴于此,对当代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总结、分析和评价,就成为一种必要。
对“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方法的方法”问题,即如何确定某种方法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以方便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具体说来,这一问题涉及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按照什么标准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是按照研究时段分类、按照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分类、按照研究地区分类,还是按照研究著作的研究方法分类?其二,在特定的标准下,如何避免重复分类的情况?相较之下,按照研究著作分类所可能面临的质疑相对小于按照研究地区或按照研究者分类所面临的问题。按照研究著作进行分类的优势在于,每一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一般只有一个,依照每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将各个著作分门别类,可以较好地避免按研究者和研究地区分类时可能造成的难于判定所属类别的情况和重复分类的情况。所谓的主要研究方法,指的是在一本著作中最为核心的、让其他方法为之服务的方法。以日本学者后藤俊瑞的著作《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②为例。后藤在书中对“存养”“忠恕”等概念在朱子伦理思想中的作用做了义理分析,并辅以对这些概念的考证疏解。由此,义理分析方法是这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本文中的分类以研究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主要依据,适时参以研究时段、研究地区、研究者的分类,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著(包括论文)为例,对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讨论。又,文中所引英文,均为笔者译;所引欧洲论著及日文论著的原版书名、翻译及简介,分别参照了陈荣捷的文章The Study ofChuHsi intheWest(《朱子学在西方》)和石立善的文章《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①。
一 考证学的方法
儒家经解传统中的考证方法主要有声韵训诂和校勘考据两个面向。对于当代朱子学者而言,朱子的著作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经”的地位,当代对朱子著作的考证研究也恰契合上述两个面向的内涵,故笔者于此借用这两个面向对当代朱子学的考证学方法予以分类描述。
(一)声韵训诂的方法。
本文所说的声韵训诂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以通晓朱子著作的文句为旨,以克服因古今、中外之别造成的语言、文化理解上的隔阂。这种传统定义中的声韵训诂法在当代的日本和欧美朱子学界都有其代表著作。
当代日本朱子学以运用传统声韵训诂方法见长。在对朱子著作的注译方面,日本学界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首屈一指的。从广度上说,日本学者注译的朱子著作包括了朱子的诗学著作、解经著作、论先贤著作、论文汇编、信札和语录集等;从深度上说,日本学者的译注在底本选择、字句翻译、文本形成背景、经典出处考证等方面大多极尽细致之功。在朱子诗学方面,比较出名的日译本有吹野安与石本道明的《诗集传全注释》(全九册)②和宋元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子绝句全译注》③。对朱子解经著作的日译本为数颇多,其中比较为学界称道的是汤浅幸孙的《近思录》日译本④,而比较流行的是吹野安与石本道明的《论语集注》日译本⑤、小泽正明的《朱熹集注论语全译》⑥以及中村璋八与古藤友子翻译的《周易本义》⑦。对朱子论先贤著作的日译本中,以梅原郁的《宋名臣言行录》的节译本①最受欢迎,另外还有进藤英幸的《伊洛渊源录》节译本②和高畑常信的《伊洛渊源录》选译本③。对朱子论文、信札、语录的汇编本的日译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友枝龙太郎的《朱子文集》选译本④、高畑常信注译的《延平答问》⑤、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⑥、市来津由彦的《朱熹〈朱文公文集〉跋文译注稿》⑦等⑧。
相较之下,运用训诂考据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是北美朱子学界的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块研究领域。这种薄弱性并不是指北美朱子学界缺乏训诂考据研究的精品之作,而是指专事训诂考据研究的朱子学著作为数甚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已故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先生的几部著作可谓其中的开山之作,另外,伽德纳(Daniel Gardner)也在这方面有精品之作问世。
陈荣捷是北美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研究的先驱。在北美学界中,他不但是首批系统阐述朱子思想的学者,也是最早以英文译注的形式在北美大力推阐朱子著作和其他中国经典文献的学者。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刊Sources of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诸源》)⑨,负责理学部分的陈荣捷摘译了《朱子全书》中关于理气、太极、天地、鬼神、人物、性命、心性、仁等内容的数十条段落⑩。1963年陈荣捷出版了大部头译作A SourceBookin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文献选编》)⑧,其中的第三十四章专论朱子,除译朱子四篇重要哲学短文之外,又选译了《朱子全书》中的二百四十七篇段落。1967年,陈荣捷又出版了《近思录》的英文译注本①,除将原文622条悉数译出之外,陈荣捷又选译了语类、文集、四书集注、或问等朱子书中的281条相关集评条目;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人和朝鲜、日本学者的评论数百条;书末更有附言详述《近思录》的编纂经过、《近思录》选语统计表、《近思录》选语来源考等内容②。这些译著内容之详尽、注解之精细,在20世纪的北美朱子学界可谓先驱之作。
如果说陈荣捷在朱子学的训诂考据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朱子全书》和《近思录》的著译,那么伽德纳在1990年出版的Learningto bea Sage: Selectionsfromthe Conversations of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学以成圣:朱熹语录分类选集》)③则是对《朱子语类》的著译精品。伽德纳在这本译著中选译了《朱子语类》第七到第十一章,并在译著的导论中讨论了朱子的文化使命感、读书之法和教学之法等内容,指出朱子读书、教学之法的核心乃是让学人于读经解经中自我发现(而不是以疏通经典文意为鹄的),进而自担延续道统的使命,这种学以成圣的读书法于今日读书人亦颇有启示意义④。
与陈荣捷相似,欧洲汉学界在朱子学训诂考据方面的贡献也主要集中于对《朱子全书》和《近思录》的译注,只是在译注的翔实和细致程度上不及陈荣捷的英文版本。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注本有:戴遂良(Léon Wieger) 教士的Textes philosophiques: Confuciisme,Taoisme, Buddhisme(《哲学文选:儒道释》)中的朱子章⑤,英国汉学家布鲁斯(J.PercyBruce)译注的《朱子全书》第42—48章①,巴黎大学博士庞景仁(PangChing-jen)对《朱子全书》第49章的法文翻译②,以及葛拉夫神父(Olaf Graf)对《近思录》的德译本③。
另一种声韵训诂法在当代日本学者的儒家经典译注中比较多见。日本学者在翻译其他中国古典文献时参考了朱子对相应文献的注解,旨在通过疏通朱子注解的方式达致对朱子所注的古典文献的理解。这是一种以通晓朱子文句为间接目的的方法,笔者也将它归入朱子学研究方法中的声韵训诂方法。在当代日本的注经之作中,运用这种声韵训诂法的名作有仓石武四郎的《论语》日译本④、本田济的《易经》日译本⑤、岛田虔次的《大学·中庸》 (1967)⑥以及赤冢忠、金谷治、俣野太郎分别出版的《大学》和《中庸》日译本⑦。仓石武四郎注译的《论语》在注释上完全参照了朱子的《论语集注》和《朱子语类》。本田济注译的《易经》以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刊本的《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注释上主要参照朱子的《周易本义》,并参以程颐的《伊川易传》。岛田虔次的《大学·中庸》(1967)⑧以朱子的《大学集注》和《中庸集注》为底本,注释上亦主要参照了朱子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朱子语类》,同时还援引了其他儒者的相关阐释①。赤冢忠、金谷治、俣野太郎三人分别注译的《大学》和《中庸》除依朱注外,还另参其他注本。赤冢忠的译本兼收了汉唐的古注②与朱子的新注③。金谷治的译本以朱注为主,另参以清儒王步青的《四书本义汇参》。而俣野太郎的译本中,《大学》部分全依朱注,《中庸》部分则以郑玄与孔颖达的古注为主④。
(二)校勘考据的方法。
在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中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并因目的不同而呈现两种面向。
第一种面向旨在确定朱子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因传抄印刷造成的多种版本中哪个本子可靠,并通过比较不同的本子来校正其中的错简衍文。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朱子学界对《近思录》的考证上。总体而言,当代的日本朱子学者大多以清儒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为底本。市川安司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对朱子《近思录》的日译本⑤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译本的校勘以江永的《集注》为底本,并校以叶采的《近思录集解》,在注解上又极尽细致之功,标出了《近思录》中各条目的出处和语句的出典,颇有参考价值。当然,也有少数的正统派继承了古代日本朱子学的传统,以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为校勘底本。如,20世纪40年代秋月胤继的《近思录》译本⑥。
第二种面向旨在对朱子解经所引典据加以分类考察,探究朱子对圣贤本意的发明。如,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1976)⑦。大槻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几乎所有的典据做了分类,将汉唐“古”注、宋人“近”注及朱子“新”注分门别类,以表明朱子优游涵泳圣贤本意的苦心。这本考证专著在出版同年即被台湾学生书局以中文版发行,毛子水在为本书中文版所作的序中盛赞其为“研究朱子学最为有用的书籍”①。
二 史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比较多见于日本和北美的朱子学著作中,致力探究朱子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梳理朱子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脉络(包括朱子一门的师承关系)、考察朱子的教育、交游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在当代大陆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多拘于哲学领域的时代,海外学者的这些史学研究方法无疑是颇为值得借鉴和参考的。这些史学研究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朱子学研究——乃至宋儒研究——中认为宋代知识分子专注于“内向偏转”、醉心于修养心性的成见,表明宋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朱子一般,积极关心参与政事和推进政治改革;同时,通过对朱子的思想及实践活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也为更好地还原和研究朱子思想的实态提供了依据。
北美方面,陈荣捷、谢康伦(Conrad Max Schirokauer)、余英时和他的弟子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这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实践活动背景做出了贡献。
陈荣捷在朱子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②:第一部是《朱子门人》(1982)③。陈荣捷在这本书中详细考察了朱子门人的人数构成、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学术贡献等,是朱子门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第二部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ChuHsi:Lifeand Thought(《朱熹:生平与思想》)④,其中收录了考察朱子投身书院教育和朱子宗教生活的两篇论文。第三部是他在1988年出版的文集《朱子新探索》①,其中收录了他考察朱子的生平、居所、衣着、游历、教学、交游友人等生活化事件的多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陈荣捷在ChuHsi:Life and Thought(《朱熹:生平与思想》)和《朱子新探索》这两部著作中,都于朱子的实践活动上颇费笔墨,这可能源于陈荣捷对1982年由他牵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朱熹国际会议的观感。参加1982年会议的学者既有当时中国哲学界的翘楚也有学界新秀,会议论文也颇具广度和深度,但是陈荣捷却在会议论文集ChuHsi andNeo-Confucianism②的编者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与会学者们“对朱熹的思想关注有余,却不够关注朱熹的个人生活”③。这就促使陈荣捷在之后的研究中努力填补这一研究空隙,发掘大量以往不被朱子学界注意的新材料,从而大大深化和细化了朱子研究的课题。
谢康伦的朱子研究也是就朱子论朱子的进路,只是他的史学研究大致拘于对朱子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考察,而不似陈荣捷那般对朱子的家事、居游等日常活动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正因为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谢康伦在研究朱子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方面用功很深,史料处理上也很细致,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献时断章取义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在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Thoughtand BehaviorofChuHsi(《朱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④中,除了参考《朱子文集》等朱子典籍,又遍参王懋竑《朱子年谱》、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等书,详细历述了朱子的政治活动(朱子辞仕致仕的经过及其政事)和政治理念(朱子的政论)。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发表了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A StudyinAmbivalence(《朱熹的政治生涯:一个两难的问题》)⑤,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The CondemnationofWei-hsueh(《受攻击的理学:质疑伪学》)①和ChuHsi's PoliticalThought(《朱熹的政治思想》)②三篇文章,其研究细化之功深得陈荣捷的赞赏③。
余英时和田浩的史学研究方法不同于陈荣捷和谢康伦的就朱子论朱子的进路,他们师徒二人更倾向于走一种更纯粹的史学研究路数,即把朱子思想放在一种综合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为研究朱子思想和道学运动的产生发展过程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在这个大前提下,余英时和田浩的研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余英时师承于钱穆,更关注朱子时代的历史政治背景,而尽量避免对朱子思想和道学运动做纯粹哲学化的抽象讨论。他在自己的朱子学代表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④中用翔实的史证说明,对朱子和同时代的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在逻辑上先于哲学思辨。他指出,道学运动远不是程朱学派一方的宏愿,而是多个道学派别交锋的结果;并且这种道学党争更多是以政见上的分歧——而不是哲学思想上的殊异——为基础的。比如,在探讨朱子继承程颐评论张载的《西铭》时由“民胞物与”概括出的“理一分殊”思想的篇章中,余英时指出,朱子对“理一分殊”的提倡是为了抗衡林栗等人对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政治内涵的质疑。林栗固守君主专制,认为民胞物与暗示的“人人为兄弟”的思想可能引发天下混乱。而朱子则认为,民胞物与、理一分殊表达了士大夫须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与君共治天下这一社会政治理想。⑤
相比之下,田浩更关注朱子时代的思想运动,对朱子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历史事实则相对涉及得少些(当然,田浩对朱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书院教育对形成道学群体的影响,道学运动成员们参与的政治斗争,等等——也有诸多探讨,只是他并不认为这些社会政治环境是左右道学运动进程和朱子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的两部朱子专著——Confucian Discourseand ChuHsi's Ascendancy(《儒家论述与朱熹之执学术牛耳》)①与Zhu Xi'sWorldofThought《朱熹的思维世界》②——中,田浩将考察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考察与朱子同时代的儒者(不仅是朱子门人)以及其他思想家在道学运动和朱子崇高地位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考察道学运动如何由最初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运动发展演变成思想运动,最终使道学在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田浩认为,不论是朱子的崇高地位还是学界所谓道学运动的一致性,都是被后世神话化的表象。田浩将道学运动分为四个思想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道学运动其领导人物各不相同,他们对“我们的道”“纯粹的儒者”“我们的学派”等道学运动中的关键字眼都有不同的理解,而朱子的崇高地位是在第三个阶段(朱子提出“道统”观念并与其他儒学派别发生思想冲突)和第四个阶段(朱子病逝后,其门人尊朱)才确立起来的③。在这个意义上,田浩认为,虽然朱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并不是自道学运动伊始就被尊为道统象征的,毋宁说,他的崇高地位是在与其思想论敌的交锋中逐渐确立的;另外,道学运动的发展史表明,朱子的道学派别所抱持的政治信念和文化诉求是在与哲学思考的互动中逐渐确立其权威性的④。
如果说北美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用于探究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实践活动背景,那么日本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着力的方面则相对更为广阔。除了像吾妻重二的《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史的地平》①运用史学方法分析魏晋玄学和佛道思想与朱子思想的相互影响并考察朱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之外,日本朱子学界的史学研究方法还用于考察朱子思想的形成脉络。其中比较经典的作品有田中谦二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②、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研究》③、市来津由彦的《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④、明德出版社的《朱子学大系》⑤等。以下简单介绍一下这几部作品的内容。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的成书灵感源于田中谦二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的朱子学共同研究班⑥。这两期研究班的成员们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作为中国古典戏曲专家的田中由此对朱子学产生了兴趣。他注意到,由于《朱子语类》是朱子的不同门人对朱子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那么,如果明确了这些门人师事于朱子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朱子思想的形成和变迁的原始轨迹。田中反复比勘《语类》中的双行小注和两名以上弟子同席记录之处,同时参考《朱子文集》及其他宋人的文集,最终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出版了至今仍被国际汉学界奉为朱子学研究经典之作的《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佐野公治的《四書学史研究》考察的是朱子创立四书学及宋明学人对四书学的发展,是四书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市来津由彦的《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朱熹思想形成的“场”——北宋末南宋初的闽北程学》——论述二程之学于两宋初期在福建的发展。第二部分——《朱熹门人、交游者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是全书的重点,考察了朱子交友、讲学、传道授业的过程。市来用小传和图表整理了朱子毕生的交游者及门人的资料,分析了朱子讲学的实态及其影响,并对朱子与何镐、廖德明等学者的交往讲学经历做了深入调查①。
相比于田中、佐野、市来等学者对朱子思想在特定时段内的形成脉络的专注,日本朱子学界的另一大部头作品《朱子学大系》的视野则更为开阔。这套由八十余位学者共同执笔的全十四册丛书涉及朱子学形成的思想背景(第一至第三卷)、朱子的主要论著(第四至第九卷)、朱子学在明清时期的展开(第十、第十一卷)以及朱子学在朝鲜与日本的研究概况和发展历程(第十二至第十四卷)。同时,这套丛书还收录了钱穆、唐君毅、秦家懿、陈荣捷等许多海外知名学者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和通论性文章,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三 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虽不似考证学研究和史学研究那般忠于朱子思想原典,却仍然是立足于原典,进而做一些义理阐发。在传统意义上,这种阐发表现为基于道统意识发明朱子思想的元素。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学术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朱子学在欧美的崛起,朱子学的义理阐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哲学思想研究的形态,表现为将朱子思想对象化并予以客观考察,其基本形态是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当然,传统的义理方法也并未因此消亡,而是有了新的目标,即坚持以朱释朱,尽量避免西方语词对朱子学的渗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传统研究式的和哲学研究式的——在当代的各个海外朱子学研究地区(日本和欧美)都不乏传承者,也就是说,20世纪前在义理分析方法上偏于传统的日本朱子学界在当代吸纳了欧美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而当代的欧美朱子学界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传统的义理分析方法。这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海外朱子学界在运用义理分析研究方法上取得的卓著成果。可以说,义理分析方法是当代海外朱子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①。
义理分析方法在日本朱子学中的影响力是与东京大学学派(以下简称“东京学派”)的贡献分不开的。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长期执教于东京大学的已故汉学专家宇野哲人及其弟子后藤俊瑞、友枝龙太郎等。在1990年以前,该学派与九州大学的体认派并称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流派。东京学派不但于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研究上建树颇多②,而且是用义理分析方法研究朱子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学派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的主要朱子学著作有:宇野哲人的《儒学史》③及其续篇《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④,后藤俊瑞的朱子哲学系列论著⑤,山根三芳的《朱子伦理思想研究》⑥,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⑦,大滨皓原的《朱子的哲学》⑧,等等。
宇野哲人在《儒学史》和《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围绕“宇宙论”“心理学说”“伦理学说”和“名分论”四个范畴展开了对朱子哲学的考察,并将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一书中,分三部分——“规范论”“德论”“实践论”——探讨了朱子的伦理思想,主要考察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成及其在朱子文本中的意义和现代意义。后藤的弟子山根三芳在《朱子伦理思想研究》中延续了后藤的思路,从道德意志论和朱子的“敬”“天”“共生伦理”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朱子伦理学。友枝龙太郎的《朱子的思想形成》讨论了朱子思想中的意识、存在、知识与实践等问题,分析了朱子知识论体系里“格物”与“反省知”“悟觉知”的关系以及朱子的格物说与他的政治实践的联系,并另辟蹊径地从朱子和陆九渊的不同生活背景为朱陆学说的差异寻找根本原因。大滨晧原的《朱子的哲学》颇有创见地提出了“理气合离”的思维方式,为化解朱子理气说中的诸多矛盾提供了依据①。
当然,除了东京学派的学者之外,日本的朱子学中运用义理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其中,走传统义理分析路数的名作如垣内景子的《「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②。垣内是日本为将《朱子语类》翻译为现代日语版本而专门成立的译注出版中心的骨干成员,也是当代朱子学中主张朱子哲学为广义“心学”③的代表人物。她的这本著作分为“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和“作为理学的朱熹思想”两个部分,考察了朱子的“心”“敬”“理”等主要概念,特别强调了朱子思想中的“心”层面,是作为广义心学的朱子学的代表作④。而采取哲学式义理方法的研究名作也有不少,如,安田二郎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⑤、汤浅幸孙的《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⑥、木下铁矢的《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①,等等。
《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收录了安田二郎四篇关于朱子的论文。安田在将朱子学文献烂熟于心②的基础上,将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于他的朱子学分析中。在其中一篇讨论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题的论文中,安田用法国哲学家Félix Ravaisson的习惯论分析朱子《论语集注·学而篇》的首章,指出朱子对“学而时习之”的解释与格物说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论及习惯在打通道心与人心、弥合“理”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的两面性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本书另一篇讨论朱子理气说的文章中,安田把朱子的理解析为“意义”,而把朱子的气描述成一种瓦斯状的气体。安田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日本学界饱受争议,但由于他的结论是基于对朱子文献的梳理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所以他的这本书至今在日本朱子学研究领域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中,精通德国哲学的汤浅幸孙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存心伦理” (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 (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考察中国伦理思想,并将朱子的伦理思想归于“存心伦理”。木下铁矢的《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则从西方哲学的理论角度对朱子的时间观、道论、易学、理学等思想给出了独特的解读③。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个误解。大陆学界多以为日本朱子学偏重于文献(主要体现在考证研究和史学研究)而缺乏对义理诠释的关注。经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日本朱子学对文献的重视是基于文献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的“第一序”的意义,即任何脱离文献解读的义理阐发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日本朱子学也并未因重视文献而忽视义理,相反,如我们从东京学派以及垣内景子等学者的论著中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日本朱子学者的著作中,文献和义理是互为支撑的,文本解读中蕴含了某种解释理论或义理分析,而义理分析也多从解读文本处着手。
北美方面,陈荣捷的《朱学论集》①和伽德纳(Daniel Gardner)的两本论朱熹解经的著作是运用传统义理分析方法的名作,但这两位学者的传统义理方法又各有特色。而孟旦(Donald Munro)则是运用哲学式义理研究方法的代表学者。
陈荣捷的《朱学论集》②延续了我们在之前介绍的他用史学研究方法写就的三本著作的理念,即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他对程朱之异的讨论、对朱子近思录的考察、对朱子仁说之来源的考证及其与张栻仁说的比较等,都是他填补以前朱子学研究空白的创见之作,虽然这本论文集不乏他用史学方法研究朱子的痕迹,如,对朱陆鹅湖之会的补述、对早期明代程朱学派的考察等,但这本书的亮点更多在于他从哲学义理方面对朱子学的研究,陈荣捷可谓“以朱释朱”的典型,他的义理分析“不用西洋名词或概念,不愿以洋冠洋服加诸朱子”③。但他同时强调本文集的意图“为申述朱子。不在宣传,亦不事辩护”④,所以又与旨在接续道统的体认式研究方法略有不同。
与陈荣捷“以朱释朱”的进路不同的是,孟旦试图把他对朱子的解读置于人性论、道德心理学等当代哲学问题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试图实现朱子思想与当代相关哲学问题的结合。1988年出版的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⑤是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论朱子的著作。孟旦在其中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朱子的人性观及其政治内涵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分析。他首先将朱子的人性观重构为四对“结构性的形象”(structural images)——家庭与流水、明镜与身体、植物与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花大篇幅分析这四对形象的意义。继而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朱子的人性观中可能蕴含的一种张力,即模仿模范的倾向(可能导向极权主义)和自我发现的倾向(可能导向平等主义)之间的张力①。由此,孟旦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见(我们可以将孟旦的这个结论与狄百瑞的朱子“心学”主张做一个对比):朱子并不相信个体之“心”有得“道”的可能,所以朱子所强调的“立志”并不具有西方“自由意志”的内涵——这可能恰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哲学根源②。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A Chinese EthicsfortheNewCentury(《新世纪的一种中国伦理学》)③中,孟旦延续了他对儒家人性论的关注,只是他转变了之前的哲学人类学视角,转而将儒家人性论与进化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的当代理论相结合,再一次对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伦理学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自然主义的解读。
伽德纳在朱子学的义理研究方面自成一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所取的似乎是广义的“以朱释朱”的进路,即不似孟旦那般将西方思想观念引入朱子学分析中,而是从注释、理解朱子典籍入手从事义理研究。但他与陈荣捷的“以朱释朱”进路也不尽相同。在陈荣捷那里,对朱子学的义理分析虽以对朱子文本的校勘注释为根据,但并不止于校勘注释。而在伽德纳这里,校勘注释(特别是对朱子解经之作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一种义理分析。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体现在伽德纳的以下两部著作中:ChuHsiand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onthe Confucian Canon(《朱熹与大学:宋儒对儒家经典的反思》)④,ZhuXi'sReadingofthe Ana-lects:Canon,Commentary,and the ClassicalTradition( 《朱熹的 〈论语〉解读:经典、注释、经典传统》)⑤。我们知道,伽达默尔(H.G.Gadamer)诠释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是,任何诠释都不可避免地与哲学上的前理解相关联。伽德纳的以上两部著作就是这个主张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详细注释朱子对《大学》和《论语》的解经著作,考察了朱子解经的前提,这些前提恰恰就是朱子哲学思想的体现,而伽德纳对这些前提的考察也恰是他对朱子思想进行义理分析的表征。在注释朱子对《大学》的解读时,伽德纳指出了朱子对“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格物”“致知”等的读解如何相异于汉唐古注,从中阐明了朱子在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上的新意。而在注释朱子的《论语集注》时,伽德纳则将朱子的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相比较,以见出朱子作为一名积极阅读者的解经策略(通过解经将自己的哲学观点注入经典中)和传承道统的使命感。通过这些分析,伽德纳让读者看到了注释经典所可能具有的原创力量(这也许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不热衷于构建系统哲学的原因之一),这种力量使解释者与被解释的经典之间——朱子与《大学》和《论语》之间、伽德纳与朱子的《大学集注》和《论语集注》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互动关系。
欧洲当代朱子学的义理方法以哲学式见长,在内容上主要是探讨朱子的神学观,这可能与耶稣会的“合儒”传教策略①有关,并经由早期耶稣会在华教士关于God与儒学“上帝”“天”之间关系的大讨论②而进一步深化。在当代欧洲对朱子神学观的探讨中,除极少部分学者否认朱子思想中存在人格神概念——如,李约瑟(Joeeph Needham)③通过详细分析朱子思想的科学倾向论证了朱子对永生与神的否定——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子是有神论者,其中对朱子神学观进行系统探讨的著名学者当属布鲁斯(J.Percy Bruce)和福克(Alfred Forke)二人。布鲁斯在他的文章The TheisticImportofthe Sung Philosophy(《宋代哲学的有神论内涵》)①中指出,朱子之理学中的理、天、太极均有宗教意味;在专著ChuHsi andHis Masters(《朱熹与其师》)②中,布鲁斯更是独立一章专论朱子哲学的有神论意义。而在福克的德文专著Geschichte der neueren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③中,探讨朱子的篇幅比探讨其他任何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篇幅都要长得多,而在对朱子思想的探讨中,对朱子的天、帝、鬼神等神学观念的研究又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然,在欧洲当代朱子学对朱子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中也不乏运用传统义理方法的精品之作。比如,之前提到的布鲁斯的专著ChuHsi andHisMasters(《朱熹与其师》)和福克的德文专著Geschichte der neueren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中,均有对朱子性命、心、仁、道等思想的研究。另外,法国人萨金静(Galen Eugène Sargent)亦在对朱子排佛论以及朱子敬义夹持修养工夫的研究上有值得关注的成果问世④。
四 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与哲学式义理分析方法有类似之处,注重引用中国哲学之外的概念和思想(特别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想)对朱子思想进行哲学分析。但与哲学式义理分析方法中引用西方概念为分析朱子思想服务的目的不同的是,文化思想比较的方法着眼点在于比较朱子思想与异质哲学体系中的相关思想,以期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彼此借鉴,开拓出哲学新路。
用比较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进路在北美和欧洲朱子学界比较流行。考虑到欧洲朱子学界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如葛拉夫神父(Olaf Graf)、布鲁斯(J.Percy Bruce)、李约瑟(Joeeph Needham)等——并未有朱子学比较研究的专著问世①,且这些学者的比较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并不具有代表性,所以笔者在本节中以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为例进行讨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英译朱子文献的匮乏,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基本停留在以西方哲学为主、朱子学为辅的阶段。以霍金(WilliamE.Hocking)的文章ChuHis's Theory ofKnowledge(《朱熹的知识论》)②为例。这是20世纪美国学界专事朱子思想研究的首篇论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遗憾的是,霍金教授在此文中大体是在西欧的朱子学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朱子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因而他对朱子思想本身的把握(以及朱子思想与斯宾诺莎、柏格森思想的比较)不尽如人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将朱子思想用作阐述斯宾诺莎和柏格森思想的工具。这种缺憾也体现在之后的朱子学比较研究论文中③。这种情况在陈荣捷诸本朱子学考证英文著作④问世之后,才开始有所改观。
大体而言,当代北美朱子学界的比较研究方法注重于发掘中西文化之间共有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这种发掘呈现出两种走向。一是发掘朱子思想与西方哲学体系相关思想(以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阿奎那、莱布尼茨、怀特海的思想最为常见)的相通处。这一研究走向比较容易流于为比较而比较,在研究深度上略有欠缺,故而只是散兵游勇式地体现于不同学者零星发表的文章中①。另一种走向是通过探讨朱子思想在西方相关话题的思想争论中所可能发挥的调解作用,从而既为西方哲学的现存困境提供可能出路,又为重新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研究走向在深度和分析的细致程度上都超过了前一种走向,因而成为从事比较研究的北美朱子学者的首选。除了许多知名学者发表的一系列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的论文②之外,白诗朗(John Berthrong)的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Whitehead,Neville,and ChuHsi(《论创造性:怀特海、南乐山与朱熹的比较》)③和秦家懿(Julia Ching)的The Religious Thought ofChuHsi(《朱熹的宗教思想》)④是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两部专著⑤。
虽然白诗朗不是朱子研究的专家,虽然朱子并不像怀特海(A.N.Whitehead)和南乐山(R.C.Neville)那样对上帝本性之类的神学话题或者上帝与创造性的关系这样的主题有过深入讨论,但白诗朗(1998)还是通过考察怀特海和南乐山在“创造性”(creativity)——特别是创造性与上帝本性的关系——观念上的分歧以及朱子对“道”(及“理”“太极”)的生生不息和“诚”“仁”等观念的阐述,颇有新意地论证了怀特海和朱子在关于创造性的观念上所可能达成的共识①。这为怀特海回应南乐山的质疑提供了契机,并为重新思考和阐述“存在”(beings/Being)、“过程”(process)、“本体论”(ontology)、“宇宙论”(cosmolo-gy)之类的西方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这种视角在客观上也为重新审视朱子学界对朱子哲学(甚至是理学传统)的通见提供了契机。
秦家懿(2000)对北美朱子学比较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该书将朱子的核心思想界定为宗教性的,将朱子的“太极”概念视为一种富有动态的、类似宗教观念中的绝对存在或终极实在的东西,并认为被朱子学界视为核心的“诚”“敬”等概念其实是为直接而无中介地领悟这种终极实在服务的。但同时朱子又通过“理”概念保持着超越向度与内在向度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一种颇为新奇的朱子学诠释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朱子学界对推崇格物致知的朱子冠以“理性主义者”的标签,转而将朱子诠释为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宗教神秘主义者(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朱子的神秘主义是即内在而超越的,而不是单论彼岸世界的)②。其二,该书将朱子的宗教思想与西方的宗教哲学传统相比照,指出朱子的宗教观不同于西方唯物论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唯知论模式(以柏拉图传统和基督教的各种诺斯底派(Gnosticism)为标志),以中道的宗教观规避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弊端③。其三,该书采用的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心理移情”诠释学模式,从而能够在对朱子文本有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重构朱子思想。秦家懿对朱子文本的语意分析极尽细致,并在分析中将朱子思想中关于鬼神、礼仪、人性、教化等的重要观念整合起来,配以对从古到今朱子批判者的考察,这种主观地重构客观朱子学(主要是朱子宗教思想)的进路使得这本书成为英文学界中内容相当丰富的朱子研究参考书。
五 体认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注重对朱子著作做客观的学术研究,相反,它关注的是通过阅读体会使自身心灵融入朱子文字背后的血脉,以道统为己任。这其实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篇》章二五),也是朱子最欣赏的一种治学态度。据《朱子语类》载:“兼是为学须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领,方不作言语说。若无存养,尽说得明,自成两片,亦不济事,况未必说得明乎?”①若没有在自身存养上下工夫,只是耽湎于训诂考据,则是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崇尚体认式研究方法的学者是最得道统真传的。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它独立出来加以讨论。
在日本,以楠本正继及其弟子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佐藤仁等为代表的九州大学一派是以体认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学者以体认(而不仅仅是研究)朱子学为学术特征,所以通常他们得出的结论颇有独到之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于朱子研究学界颇有影响力。遗憾的是,虽然荒木和佐藤仁至今仍活跃在学术一线,但如今的九州大学汉学界已鲜有人继续以体认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了。鼎盛时期的九州学派运用体认研究方法的代表作有②: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③、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④、冈田武彦的《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⑤等。
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享有广泛声誉,是对宋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分为“宋学”和“明学”两部分,其中“宋学”部分论及了朱子,其中多有见解独特之处。如,楠本将朱子思想体系概括为“全体大用”四个字,并将朱子推行社仓法的政治作为与全体大用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政治作为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①。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是儒佛思想相互影响的一个绝佳范例,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架构展开,其间不乏妙思。如,在比较朱子与南宋著名禅师大慧宗杲在思想上的异同时,荒木敏锐地注意到了朱子“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思想中蕴含的关于日常性的思考,认为这种思考比大慧宗杲标榜的证悟主义更有实践性,可以规避禅修体验中超乎人情、世情而可能造成的弊害②。此书虽涉及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但这种比较中贯穿着九州学派辩护朱子的精神,所以笔者仍将之归入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之列。冈田武彦虽然是阳明学的倡导者,却难能可贵地对朱子学有诸多同情的了解。他于《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中发表了五篇专论朱子的论文。这些研究为冈田运用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出版论著《作为活学的朱子学》③)、探究儒学的经世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学者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是实践儒家为己之学的代表人之一。从Neo-Confucian Orthodoxyand theLearning oftheMind-and-Heart(《宋儒正统与心学》)④中通过考察朱子的道统理念来强调个体的“自任于道”,到TheLiberal TraditioninChina(《中国的自由传统》)⑤中将儒家提倡的自主人格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做一衔接的努力,再到Learningfor One's Self(《为己之学》)⑥中对“己”和“道”关系的探索,以及The TroublewithConfucianism(《儒家的困境》)⑦中对儒家人格和君子之道的讨论,狄百瑞念兹在兹的是儒家道统的普世价值和个体传承道统的可能性。撇开狄百瑞通过宋儒的精神风貌探求儒家普世价值的进路是否可行的问题①不谈,单就狄百瑞对宋儒精神风貌特别是对朱子在界定道学正统上的重要作用的考察来说,狄百瑞的研究还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朱子强调个体内省之“心”如何“居敬”以使先知(prophet-ic)启示之“道”化育于自我,并由此把“道学”视为“心学”,突出了朱子“道学”中的宗教意味②。
六 其他方法
(一)索引的方法。
应该说,当代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是与对朱子文献的索引编纂工作分不开的。朱子学中的索引方法指的是从朱子著作中摘出重要术语,著录成按一定检索顺序排列的简明条目,并注明该条目在原著中的页码,以方便研究者搜集、查找和研究朱子原始文献。这方面的研究属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后藤俊瑞编纂的“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包括了《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与《诗集传事类索引》③三种)、佐藤仁编纂的一系列索引(《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④、为《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⑤中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编制的人名索引以及为《中日合璧版朱子语类大全》⑥编制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以及东京大学朱子研究会的二十余位成员经过十七年辛苦努力编纂而成的大型索引《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⑦都是其中的精品。
(二)疑古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本应属于广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但由于这种方法并不以还原朱子思想的实态为旨归,而是以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批判朱子思想,检视朱子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所以笔者将这种方法从史学研究方法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考察。
自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津田左右吉开创这种研究方法以来,当代日本的朱子学界乃至宋明思想研究界不乏这种思想的追随者。津田本人受中国清代学者崔述的“疑古辨伪”思想和德国史学家Leopold VonRanke创立的兰克史学派的双重影响,以疑古和史料批判为纲,以质疑、批判中国和日本古典文献记载内容真实性为己任。与其师白鸟库吉从事满蒙地理研究和西域研究不同,津田对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史颇感兴趣,并将疑古批判式的方法带入了他的中国思想研究中。虽然津田本人并未将疑古批判的方法专门用于朱子研究,但土田健次郎和小岛毅等学者则将这种方法延伸到了朱子学研究领域。土田健次郎在《周程授受再考》①中,否认朱子关于二程师承于周敦颐的说法,主张二程是道学的实际创造者。而小岛毅则为土田的书所写的书评《“周敦颐神话”的崩壊》②中,全然支持土田的立场,甚至不无戏谑地对朱子的学术人格提出质疑。虽然有日本学者对这种过分轻视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异议③,但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青睐的大有人在,更有学者以此为契机,指出当代日本宋明思想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脱离神话主义”④。
应该承认,这种疑古批判式的研究方法的确有其自身优势。相比于某些“崇朱”的研究方法,疑古批判的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突破朱子设定的视野,回归历史真相,凸显研究者自身的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潜在的危险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危险性远大于疑古批判具有的研究优势。过分地强调对朱子视野的突破可能导致在未深入朱子语境的情况下妄下论断,乃至揶揄前人、失之轻妄而不自知,这既是严谨治学的大忌,又偏离了疑古批判研究方法的本意。
(三)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着眼于在现实中运用朱子著作所蕴含的道理,以求为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哲学诠释学主张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①过程充分表明,通经致用是经典诠释(主要是义理分析方法)的题中之意。笔者在本文中将通经致用的方法独立出来,是为了强调这种研究方法在追求用世的前提下所可能导向的治学大忌,即得鱼忘笙地主张对经典做超出其文本范限的解读。在今日学界日益盛行的用世风潮中,保持对上述治学禁忌的警醒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而海外朱子学界运用通经致用方法的名作无疑为我们学人保持这种警醒提供了极好的范例。除了之前讨论诸种诠释经典方法时提到的相关著作(如孟旦的论著)外,冈田武彦的《作为活学的朱子学》②和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③的第三篇(“实践论”)中对“恕”概念的现代意义的探讨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四)意识形态式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指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术语和思想用在朱子学研究中,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颇为盛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之一④,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力量真正成型却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至70年代①。受此影响,这段时期内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也出现了用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分析朱子思想这一分支。代表著作有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②以及守本顺一郎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1967)③。岛田虔次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把朱子和阳明思想放在同一个思想史脉络中进行描述,并分别冠以“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称谓。而守本顺一郎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随处可见“丸山政治学”④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丸山将朱子学定位为封建思维在中国的完成形态及其对朱子的生产论的阐述等都可以被解读为守本朱子学研究采纳上述两大思潮思考模式的结果。
以上,我们通过对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主要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予以分析、提炼,总结出了考证、史学、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体认式等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并非截然相分,它们彼此间有交集。比如,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之间就有可能重合之处,这是因为,研究者在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朱子思想的哲学阐释时有可能需要借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和思想,从而涉及运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再如,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与考证的方法、史学的研究方法、哲学义理式的研究方法、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等之间亦有交集。因为体认式的研究可能以考证、史学研究、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等方式呈现出来,也可能以通经致用为最终诉求。另外,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方法也可能是相互结合的。比如,信广来(ShunKwong-loi)就主张一种由考证而义理的方法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方法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节 韩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②
一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传入朝鲜,经过高丽王朝时期100多年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到14世纪末成为朝鲜李朝的建国理念(即官方哲学),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对此后500余年间朝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期,为朱子学的初传阶段。嘉定十七年(1224)春,朱熹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等到达高丽全罗道的锦城,建立书院讲学,传播朱熹思想,这是朱子学在朝鲜民间传播之滥觞。而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引起统治者重视的则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安垧、白颐正等人。安珦(1243—1306)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朱子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教之正脉,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横经受业者动以百计”。③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④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1298年随忠宣王到元大都燕京,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大量程朱理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珠(颐正)。”①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颇有建树。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
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之所以会在此时传入朝鲜,一方面与高丽同元朝的密切关系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有关。可以说,正是朱子学北传并在元朝取得统治地位,加之高丽同元朝频繁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为朱子学流入高丽疏通了渠道,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程朱理学在中国产生时,汲取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适应了朝鲜三教并存的历史与三教合流的趋势也为其移植朝鲜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二是14世纪下半期,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阶段。安珦、白颐正等先驱者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开启了高丽朱子学之先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更多地还只是停留在对程朱理学著作的介绍和引进上,还来不及对程朱理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和发挥,而且传播的规模尚局限于高丽上层极狭小的范围内。进入14世纪下半期,由于朱子学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李朝开国后朱子学正式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推动朱子学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
李穑(1328—1396)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李齐贤(1287—1367)是权溥的女婿,曾跟随忠宣王滞留元大都30年,其学注重程朱的“敬以直内”,反对佛教和汉唐经学。李穑年轻时,曾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学者皆仰慕。掌国文翰数十年,屡见称中国”。③官至宰相。他在成均馆任大司成期间,以朱子学为教育内容并对《小学》作谚解,进行普及,任宰相期间,笃力推行儒学教育,在中央建五部学堂,地方设乡校。史载:恭愍王十六年(1367)“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威,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土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月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尘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①后来对朱子学有创见发挥的学者如郑道传、极近等,多出自李穑门下。
郑梦周(1337—1392)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②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③他对朱子学的阐发,同代人颇为折服。“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④李穑曾高度评价郑梦周:“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⑤
郑道传(1337?—1398)号三峰,他不仅是高丽两班改革派的干城,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理论基础的奠基人。他“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鸣孔孟程朱之道学,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邪说,明天理正人心吾东方真儒一人而已”。⑥权近(1352—1409)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受到郑道传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论。权近的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五经浅见录》是继承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李朝时期刊行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溯其发端盖出于权近的《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更是远及日本。
这一时期的高丽朱子学,正是经过李穑、郑梦周、郑道传及权近等的大力推动,加之它适应了当时改朝换代的社会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新王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李朝(1392—1910)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1392年李朝开国。李朝统治者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李朝开国到1876年日本势力入侵朝鲜的近500年间,朱子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甚至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也只有借助朱子学的外衣才能存在。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为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到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
退溪学的代表人物李滉(1501—1570),字景浩,号退溪,是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退溪集》(68卷)、《朱子书节要》、《启蒙传疑》、《心经释象》、《天贫图说》、《四端七情论》等。李退溪终身尊信朱熹的思想和学问,武夷山是朱熹晚年弃官隐居和沈潜学问的地方、陶山是李退溪隐居的地方,自古以来又叫作武夷。1183年4月,朱熹54岁时,在武夷山建盖了精舍,翌年写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因物寄兴,沿着武夷山的九曲描写了名胜和景物特色。退溪阅读了《武夷山志》之后,从想象中游览了朱熹隐居的武夷九曲,继承了朱熹《武夷棹歌》的形式,写了《次武夷棹歌》十首,引端了后来韩国各地指称九曲的潮流。如18世纪后期李野淳等人进行的陶山九曲的设定和有关诗歌的创作,他的《陶山九曲》诗次韵朱熹的《武夷棹歌》,又把李退溪的《次武夷棹歌韵》的意向当基础,描写了陶山一带的山水风光。退溪的《武夷棹歌》和韵不仅形成了韩国诗歌史的传统脉络,而且退溪学派的人往往把陶山九曲看成想象武夷和学习朱子的体验空间。①在哲学上,李退溪直宗朱熹,持“理一元论”观点,主张理贵气贱说和理气互发说,重视实践意义的“敬”,强调世界万物产生于“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动静乎”。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先知后行”,强调“性”有纯善无恶的“本然之性”和善恶不定的“气质之性”之区别,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启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之先河。其所创建的陶山书院,至今仍是韩国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书院。退溪学目前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由首尔退溪研究院创办于1973年的《退溪学报》,至今已经发行了一百多期。由退溪学釜山研究院创办的《退溪学论丛》至今也已发行了十余辑。退溪学国际会议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以上。韩国首尔和釜山、日本东京和福冈、中国北京以及香港和台北等城市都曾主办过研讨会。退溪性理学、退溪诗学等相关专题的研究始终都是学界的热点。
这一时期朝鲜朱子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李珥。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世称栗谷先生。1558年去陶山拜李混为师。1564年考中生员、进士科和明经科,历任户曹佐郎、吏曹佐郎、户曹判书、大提学等官职。在因病辞官期间,他回到地方专心从事书院教育事业,著有《栗谷全书》44卷。李珥反对“理气互发论”,主张“理气兼发论”,创立了朝鲜朱子学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他认为世界是由“气”和“理”所构成,“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理气“浑沦无间”,“实无先后之可言”,同为世界万物之源。但他又认为如论理气先后之分。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官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反对李滉在“性”“情”上的“四七说”,提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认为七情以外无四端。李滉、李珥的“四七论争”,开拓了朝鲜朱子学的新领域,后与李滉一起并称为朝鲜思想界的“双璧”“二大儒”。
以李滉为中心的岭南学派(主理派)和以李珥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气派)的论辩持续了长达三百年之久,而这也是朝鲜朱子学的成熟期和巅峰期。到了16世纪末,朱子学逐渐从学术论辩转到与理论研究无关的“礼论”等问题,甚至成为争权夺利的党争工具。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畿湖学派分化为“老论”和“少论”。“老论”学者将朱子学化为绝对理念,并以自己的理论为朱子学正统。“少论”学者则反对朱子学绝对化甚至批判朱子学,还出现了郑齐斗(霞谷,1649—1736)这样的朝鲜阳明学大家。与此同时,岭南学派中则出现了“实学”之风,从“利用厚生”的观点来批判观念化的朱子学,谋求儒学的新方向。如以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的“实事求是学派”,主张在研究经典时依确实的考证,理解文本真正的意义;以李翼(星湖,1681—1763)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关心土地制度和行政改革)和以朴趾源(1737—1805)为中心的“北学派”(振兴农业、主张工商业的流通和生产技术革新)则主张理论研究要对现实社会的文物制度和社会文化政策有贡献。实学派观点的集大成者是丁若镛(茶山,1762—1836)。他主张土地和社会制度改革,重视科技,这既使朝鲜从性理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也间接加速了朱子学在朝鲜的衰落。
二 当代韩国的朱子学的研究
(一)20世纪初的朝鲜朱子学。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面对西学的渗入,朝鲜朱子学内部分化为传统论派、开化论派和调和派。三派的思想特点及其研究方法大致如下。
传统论派开展卫正斥邪运动,有原教旨主义的特点,大都奉行尊华攘夷的义理思想,秉持朱子“理尊气卑”的形上学,视儒学为理、为王道,西学为气、为霸权主义。按照朝鲜朱子学思想体系的两大派——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①——来划分,岭南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震相(号寒州,1818—1885)、张福枢(1815—1900),畿湖学派中的传统论代表学者有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柳麟锡、田愚(号艮斎,1841—1922)、朴世和(1834—1910)等②。由于我们的关注点是当代朱子学,这里将略去对几位19世纪的传统论者思想的考察,而关注柳麟锡、田愚这两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论者的思想。
柳麟锡主张,儒者在国家变乱之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态度:第一,发起义兵以扫清逆党;第二,即使离开国土,也要守住旧制度;第三,奉献生命以遂成其志。③他的理论依据是理尊气卑、理主气客的思想。他指出,“其所本者理,所形者气,而理气元是帅役上下”①。但他的兴趣点并不在讨论理气的关系,而在于以此为依据,强调民族自主和确立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批判当时朝鲜的西化倾向。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五伦”乃是据于天理,而西方的新教育则只是追求形气以满足欲望,因此是应当拒斥的。另外,西方新教育的推行是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之一,所谓的西化不过是日本希望引导朝鲜脱离清室、逐步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实现韩日合并的奸邪诱饵。
类似地,田愚的研究也是将性理学作为理论基础,而着眼于解决当时韩末的社会危机。不过,他的性理学主张与柳麟锡的有冲突。在《两家心性尊卑说》(1918)一书中,田愚指出了他的性理学主张与其他学派的主张的不同:他主张“性理心气论”,认为心是气而不是理,因为心并非静而无为,而是动而有为的;相比之下,其他学派则主张心主理,而没有看到心须依理合理才能无偏失的道理。在此基础上,田愚在《从重时中辨》(1905)一文中指出,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体现“性即理”说,而夷狄和异端则只能随“心即气”的欲望思考和行为②。与此相呼应,田愚在《与郑君祚》(1877)③、《论裴说书示诸君》(1908)④等一系列书信中提出,应对当时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当权者作性理学的内圣修养,并施行排斥夷狄之开化论的政策。随着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加剧,田愚选择了隐遁守旧而力保华脉,将余生奉献给了朱子学乃至中华文化的教育和写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论派主要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即他们对朱子思想和著作的讨论是以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为旨归的。
再来看开化论派。秉持开化论的学者们⑤积极接受西方新学(主要是天赋人权思想和社会进化论),批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的无用性,提倡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甚至将被日本殖民的亡国原因归咎于儒学,以为朱子学空谈心性,阻碍智力发展,并以腐朽思想求生存,实乃缘木求鱼①。
最后来看调和派。调和派由一些活跃于政界的儒者组成,提倡以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体新用论或儒体西用论,反驳开化论对儒学的批判,认为开化不是无条件地仿效西方,而是要适合自己社会的现况。这一派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如朴殷植、金允植,等等)是韩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②。调和派鲜有朱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是持批判朱子学的立场的。其中,朴殷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朴殷植在早年(1859—1897)属于传统论派,仅以朱子学为正学。在经历了甲申政变(1884)、清日战争、甲午更张(1894)等事件之后,朴殷植看到了传统论派在对抗日本侵略上的无力性,遂转而批判朱子学。他一方面创立“大同教”(1909),作为儒家改革的主体;另一方面,推广阳明学,批判朱子学。在《儒教求新论》(1909)一文中,朴殷植指出了朱子学的三大弊病:第一,朱子学只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工具,与儒家的根本政治思想(民本主义和大同主义)相背离;第二,朱子学只是消极布教的权威主义而已,偏离了孔子周游列国思以易天下的理念;第三,就学问本身来说,朱子学支离繁杂,所讲的“知”与新学的科学之知是同一知识层次;而阳明学的良知则高于科学知识,可以吸收各种科学,纳于良知之学内。③类似于传统论派,朴殷植也同样运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只是他的通经致用方法是从批判朱子学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朱子思想,比如,将朱子学在现实运用中的教条化归咎于朱子思想本身,并将朱子的“知”等同于闻见之知。
(二)1905—1945年的朝鲜朱子学。
1905—1945年期间,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朱子学作为朝鲜本国文化传统的代表而遭到了歪曲①甚至废止,这令20世纪初传统论派的复兴朱子学努力严重受挫。朱子学乃至儒家文化都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处于低谷期。尽管如此,一些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却仍致力于延续朱子学和儒学的命脉。这段时期内比较著名的朱子学和儒学成果有: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何谦镇的《朱子書節要》(1939)、《东儒学案》(1943)。
张志渊的《朝鲜儒教渊源》(1922)是韩国首部近代儒教通史。张志渊曾任《时事丛报》《皇城新闻》的主笔,并在满洲条约签定时,发表社论《是日也放声大哭》(1905),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在《朝鲜儒教渊源》一书中,他受到韩国实学的影响,将奉行朱子学抽象理论的性理学家斥为小人儒,与他所推崇的李翼(星湖)、丁若镛(茶山)等君子儒区分开来,认为朝鲜李朝衰亡原因是因未用君子儒或真儒。他既批评传统论派不知变通、拘泥于性理和训诂,又批评开化论派不懂得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盲从西学之浅表,认为二者均失其中,主张儒教伦理与近代科学可以参互变通。他表示,西方的科技是近三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故论古代文明,则东方优于西方,只是旧儒们拘泥固执,而使儒学浮虚无灵,才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衰落。
何谦镇(1870—1946)堪称以道统为己任的典范。他本人曾以儒者身份参与独立运动,并两次入狱,并于1931年创立“德谷学堂”,晚年著书立说,致力培养后学。他的《东儒学案》(1943)可以算作朝鲜儒学史上唯一的学案。朝鲜儒学史上类似的著作是朴世采的《东儒师友录》(1682)和宋秉瑄的《浿东渊源录》(1882),但在影响力上皆不及《东儒学案》。《东儒师友录》包括了薛聪以下的750位学者,但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他们的师友渊源和行迹的,而不是关于思想。另外,这些被选择的人物大都是畿湖学派的学者,时代也局限于18世纪后期。《浿东渊源录》参照了朱子《伊洛渊源录》的体例,兼参《东儒师友录》,主要记述人物的思想渊源,多引用关于人物行迹的材料,而不是人物的思想观点,且未区分学派。相比之下,《东儒学案》则要全面很多。《东儒学案》分为上、中、下三册二十三篇,每个学案里,都包括学派来源、代表学者的生平和学问特性、思想特色等内容。何谦镇以道统论的观点成书,认为理学为儒学正统,并以朱子学为理学正统,以退溪学派为中心。尽管本书重视道学义理实践、而不注重性理学的哲学理论和各学派的学问异同,从而未论及朝鲜阳明学派(江华学派),但是全书对各个理学学派的分殊和脉络均有细致而公允的分析和评价,这使得此书的分类构图一直为人所称道,也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不失为研究韩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一项重要参考文献。
(三)20世纪40—70年代初的朝鲜朱子学。
1945年之后,朱子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处于低谷期。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在经历了促进韩国近代化进程的甲午更张运动以及日本实行的彻底抹杀韩国传统文化的政策之后,中断的文化传统已很难迅速复苏。第二,光复之后的韩国处于文化过渡期,而朱子学没能通过自我改革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力与其他各类文化竞争,当然也不能主导韩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三,美国军政时期(1945—1948),西方文化渗入,致使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很难一枝独秀,韩国民众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很难对朱子学有亲近感,加之韩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逐渐西化,仅有极少数韩国大学维持朱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命脉。第四,韩国政府和民众都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富裕上,进一步造成了传统伦理价值的危机。第五,在经历朝鲜李朝崩坏、日本殖民统治之后,20世纪的韩国基本上每十年有一动荡,50年代南北对峙、60年代学生民主革命和军事政变、70年代实施巩固维新独裁体制,韩国社会处于长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中,这对于20世纪初就岌岌可危的韩国朱子学来说,无疑又是新的挑战。特别是50年代的南北对峙以及60年代实学思想的复兴(克服朝鲜朱子学空谈心性的倾向,力求回到原始儒学的质朴面貌,兴起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都是对朱子学研究的阻碍。
1945年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论著有:玄相允《朝鲜儒教史》(1949);李丙焘《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1959)以及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郑寅普、李相殷的著作。
玄相允的《朝鲜儒教史》采用文本考据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朝鲜朱子学两大富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对峙为主线,勾画出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脉络。李丙焘的《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则采用了史学研究方法,考察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朝鲜的发展轨迹,着重于梳理这两派在朝鲜的历史流变,而不是进行思想分析和论述。
郑寅普和李相殷的著作可以被看作韩国现代新儒家的两大思想体系——阳明学现代新儒学和朱子学现代新儒学——之间的争论的绝佳范本。同为韩国现代新儒家,两大思想体系皆主张兼采东西学术之长,综合新旧之学,但对何为东方学术之长的问题有争议。郑寅普著有《阳明学演论》①,继承了20世纪初的朝鲜阳明学家朴殷植的批朱立场,认为阳明学与朝鲜民族意识能自然结合,圣贤之道在于人心未亡,而其人情自身则是至善良知的表现;而朝鲜儒学流弊则生于朱子学,朱子学或讲论心性而少于己身的良心契合,或标榜道义却以此图谋私利②。李相殷则是朱子学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他著有《〈大学〉〈中庸〉之现代的意义》《再论东洋文化》《从humanism看儒教思想》《批判国史教科书之性理学叙述》《儒学与韩国思想》③《四七论辩及对说、因说的意义》④等,旨在匡正对朱子学的流俗偏见,并试图熔铸朱子学与现代学问。类似郑寅普,他也提倡修正儒学重义轻利、内本外末的思想,主张兼顾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但他认为朱子学的性理之学并不像阳明学者理解的那样与现实生活相疏远,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的,从而实学并不与性理之学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无实学之性理学为空虚,无性理学之实学为盲目也。”⑤具体说来,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当今价值在于三方面,其一,看到制度的制定和改革并非万能,制度操作者的道德性更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教义是基础;其二,西方的历史呈现出对立分裂形态,而儒家则提示出一条合作、统一之道,比如,秦、汉统一就与儒家的政治哲学经典《大学》和心性哲学经典《中庸》的出现关系密切;其三,肯定朱子对《大学》的格物释义,认为其具有科学精神,可以视为清代实学和韩国实学的鼻祖,朱子学较之陆王学,具有更踏实的学风和现代意义。
(四)多元化时期的朝鲜朱子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韩国社会的国际化,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开始流行,其中不乏正视传统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在各个大学重视复兴传统文化、增加研究人员以深化学术研究的风潮推动下,为朱子学的复兴带来了新的生机。韩国学界甚至兴起了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并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韩国学者梁承武(2008)的统计,从80年代开始,有关朱子学方面的单行本、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等各类论著较80年代前有了极大增长,而研究广度也极大提升①。就广度来说,这些研究涉及了朱子及朝鲜历代朱子学大家的哲学思想(以理气论、工夫论等方面的研究业绩较为丰厚)、散文和诗歌研究、教育思想,等等。然而,从研究的深度来说,70年代之后的朱子学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大多数研究都缺乏思想上的创新意识,而以客观、逻辑性的思想史研究或文本研究为基本特征,即只停留在研究朱子和历代朱子学大家的思想、论著和言行的层面,把儒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从70年代至今,涉及韩国朱子学史研究的论著及论文主要有:裴宗镐《韩国儒学史》(1974)②、《韩国儒学资料集成》(1980),李东俊《关于17世纪韩国性理学派历史认识的研究》(1975)③,韩永愚《朝鲜前期性理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1976)④,柳承国《韩国的儒教》(1976)、《东洋哲学研究》(1983)⑤、《韩国儒学史》(1989)⑥,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1980)⑦、The Korean Controversy over ChuHsi's ViewontheNatureofMan and Things(《韩国学界关于朱熹论人、物之性的争论》,1982)①、《东洋思想与韩国思想》(1984)②、《退溪李滉的哲学思想》(2000)③,权延雄《世宗朝的经筵和儒学》(1982)④,李楠永《理气四七论辩与人物性同异论》(1984)⑤,琴章泰、高广稷《儒学近百年》(1984)⑥,金忠烈《高丽儒学史》(1984)⑦、《韩国儒学史》(1998),李成茂《朱子学对十四、十五世纪韩国教育及科举制度的影响》(1986)⑧,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 (1986)⑨、 《韩國儒学史》 (1987),玄相允《韩国儒学史》(1986)⑩,崔英辰的五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史》(1997),姜在彦《韩国儒学两千年》(2003),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室编的七卷本《韩国儒学思想大系》(2005—2007),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2008)⑪,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2011)⑫,等等。其中也不乏研究韩国大儒的思想的论著,如韩永愚《郑道传思想研究》(1983)⑬,李东翰《技术之危机与敬哲学之解答》 (1988),申龟铉《西山真德秀之〈心经〉与退溪李滉之心学》(1988),李基东《李退溪的人道主义和敬》(1988),丁淳睦的《朱晦庵和李退溪之书院教育论》(1988)⑭。还有一些是比较韩国儒学与其他国家儒学研究状况的论著,如,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1995)①。
这些论著主要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梳理朱子学在朝鲜的发展脉络(或某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或者横向考量朝鲜朱子学研究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朱子学研究之间的异同。比如,裴宗镐(1974)探讨了朝鲜性理学的主要议题——四端与七情论辩及理气论争——的演变过程及论争的焦点所在;柳承国(1976,1989)探讨了朱子学传入高丽的经过以及朝鲜性理学的兴盛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尹丝淳(1980,1984)则以对韩国儒学的特性为分析主线,探讨了韩国神话传说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的权威地位的关系(他认为,韩国神话传说揭露出韩国文化对于超越问题的兴趣,使得性理学家对于朱子学中的“天命”“天人合一”“穷理”等问题有细致的、突破性的讨论)、朝鲜前期和后期思想家对于“实学”和“虚学”的看法的不同(朝鲜前期儒者以佛学为虚学、性理学为实学,后期实学派则以超越训诂和辞章、袖手谈心性的性理学为虚学,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之学为实学),等等。有时,这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以客观叙述为旨归的,而是带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这种研究带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论预设,比如,金忠烈(1984,1998)的儒学史叙述是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儒学并非宗教,不认同来世,而是追求现世的现实主义;而琴章泰(2011)则主张,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并从朝鲜历史上积极实践儒学价值的儒学家的具体功绩研究入手(比如张志渊、何谦镇等儒者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奔走、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等),研究儒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第二,这种研究方法是与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比如,李东翰(1988)、申龟铉(1988)、李基东(1988)、丁淳睦(1988)都是试图通过将研究退溪思想与探讨其现代意义结合起来,为现代社会确立价值目标。不过,从总的研究倾向上来看,大部分采用史学研究方法的论著还是从客观的角度切入的。
除了对韩国朱子学史的研究,70年代之后的韩国朱子学研究也涉及对朱子本人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训诂考据的方法;二是义理研究的方法;三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了训诂考据方法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朱子论著的韩文注译工作。根据梁承武(2008)的考察①,在韩国出版发行的朱子学译著主要有《四书集注》、《小学集注》、《诗集注》②、《朱子家礼》③、《朱子家训》④、《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到卷六“性理三”部分⑤、《近思录》⑥,等等。至今,尚无朱子全套著作的完整韩注本问世,甚至一些朱子的重要著作(如,《四书或问》《仁说》,等等)亦未有韩注本。
运用了义理研究方法的朱子学研究代表作是金永植(Yung SikKim)的一系列朱子学著作。由于他的研究以往较少被讨论到的朱子自然哲学为关注点,发前人之所未发,笔者拟用一定篇幅介绍他的研究内容。
金永植在2000年出版了专著TheNatural Philosophy ofChiHsi(1130—1200)(《朱熹的自然哲学1130—1200》)⑦,研究朱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将朱子的自然哲学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相比较。他首先讨论了朱子自然哲学中的基本概念——理、气、阴阳、五行、象数,等等,并兼论鬼神、天和圣人这些虽“不属于自然世界、但仍与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有关”⑧的事物。接着,他讨论了朱子对自然界的一些论述,比如对物质层面的天地的看法、对万物的看法(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对人的物理、精神、生理各方面的理解。最后,他从与中西方科学传统出发,考察朱子的自然哲学概念和对自然界的论述,比较二者的异同。
金永植在2009年发表的《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①一文中指出,朱子对“自然科学”(天文、历法、医学)和“超自然主题”(如,占卜、风水、内丹、祭祀,等等)均有大量研究,认为它们既是他“格物”学说的体现,又是出仕儒者需要涉猎的课题(因为它们可以增进百姓社稷的福祉)。金永植的文章从以下三方面讨论了朱子对科学和超自然主题的研究:第一,朱子对当时流行的文本做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和注疏,编辑相关著作、确立正确意义、校正错误甚至更动原文,并确立学者应研习的最佳读本。第二,朱子赋予超自然主题以合理性,认为它们并不违背儒家的基本立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气”的概念以及气与心的交互作用为这些超自然主题提供了理据,比如,内丹和风水等技术之所以养生,乃是因为“气”本身的生命特质以及心对人体外阴阳之气的掌控能力,另外,卜筮和祭祀中还涉及人心与天地之气或祖先之气的相互感通。其次,朱子批评同时代的儒者专研《易经》的义理而忽略其占卜面向,指出《易经》卜筮是一种重现宇宙过程的活动,《易经》是联结人体与宇宙运转的主要工具,而占卜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转。第三,朱子对当时超自然的奇异事例时保持开放态度,但将它们归因于气的性质和活动,而不是直接承认有超自然的存在体与力量。金永植还分析了朱子的这种开放态度的产生原因:朱子对智力挑战的兴趣、朱子对自己在许多学科上的卓见自信,以及朱子对古代知识的一贯尊崇。金永植最后总结说,由于朱子对科学与技术的主题给予了足够关注,使得儒学更为完备和开阔,并具有了科学精神;同时,朱子对超自然主题的涉猎,也相对缓和了他的理性主义立场,同时使他的哲学体系更为完备和富有解释力。
梁承武的博士论文《朱子哲学思想之发展及其成就》(1984)是史学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本。该书以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义理内容为中心,讨论了先秦、北宋儒学与朱子思想的师承关系、朱子关于中和问题的论定、朱子关于仁说的论辩、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及理气论以及朱子哲学可能为现代哲学讨论贡献的话题,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该书是当代韩国学界为数不多的对朱子本人的哲学思想予以全面述评的专著,但是从内容上说,这本书却没有太多新的建树,基本上未超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朱子的判教。
(五)小结。
综观之,当代的朝鲜朱子学界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相比于对朱子本人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当代朝鲜朱子学界更重视对朝鲜历史上的朱子学研究大家的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其二,相比于朱子学在朝鲜时代传统社会拥有的绝对影响力和权威地位,当代的朝鲜朱子学乃至儒学已经萎缩,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文化思潮之一。其三,与朱子学的地位变化相伴随,在朝鲜李朝时期成果迭出的对朱子学中的理气心性及人物之性同异等思想的探究和发展,被客观的思想史研究以及为朱子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寻求根基的探讨所替代。
这三个特征在当代朝鲜朱子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有体现。20世纪初,朝鲜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论派和调和论派的学者大都采用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运用朱子学著作的理论为现实困境找出路。1905—1945年的日本殖民时期,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朝鲜传统文化岌岌可危,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多运用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以道统为己任,使自身心灵融入朝鲜朱子学的血脉,张志渊、何谦镇等朱子学者的朱子学研究著作中均有很强的道统意识,致力于延续朝鲜朱子学命脉,且他们本人也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实践传统文化。1945年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朱子学的情势虽不及日本殖民时期的灭顶之灾,却仍十分严峻,主要原因之一乃是韩国社会对于朱子学的文化价值产生了质疑。这一情形与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出现的朱子学危机多有类似之处,于是,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也就类似于20世纪初的朱子学研究,即说明朱子学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决定了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在这段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嗣后,复兴传统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朱子学面临的危机逐步缓解,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多样化,但是,韩国社会的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子学权威地位不再的事实,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也转而以客观的史学研究和训诂考据研究为主(虽然偶有义理分析的研究著作,却毕竟不是主流),缺乏新的理论建树。
第三节 越南及新加坡的朱子学研究
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时段:19世纪末期,新加坡曾出现过儒学热,甚至被标榜为“儒学复兴运动”①。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在新加坡创办了一系列华文学校(“崇文阁”“萃英书院”“养正书室”,等等),旨在“究洛闽之奥”,并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作为教材②。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儒家伦理教育,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旨在推动儒学在新加坡的复兴。但是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更多的是停留在“通俗儒学”的层面,即作为一种华人道德价值观存在于普通民众中,并以家庭环境熏陶的方式留存。19世纪末的儒学热被五四思潮浇熄,20世纪80年代的儒家伦理教育也仅持续了8年时间,无疾而终(1990年,儒家伦理课程被公民与道德课程取代,东亚哲学研究所也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③。更重要的是,学术层面的儒学研究在新加坡极少专门涉及朱子学,鲜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成果问世。
管见所及,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道运曾经专门从事过朱子学研究。作为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他对朱子学有相当深的研究,著有《朱学论丛》④《日儒林罗山(1583—1657)的朱子学——着重对其教育思想之研究》①《朱熹心学的特质》②等。他主要运用的是以考证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尽心工夫的角度切入朱子理论体系的研究,并兼对元代南北方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的思想以及日儒林罗山的教育思想有深入探究。他指出,朱子的心性践履之学乃是朱子心学的主要特征,体现了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并不相分。朱子由尽心工夫体会心不即是理(因为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与气之上),这是朱子对儒家心学的特殊贡献。类似地,元代的几位朱子学者也遵循了朱子由气质切入切实践履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他还指出,这种朱子式的心学对今日道德修养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提示我们需依本身气质所近而从事切实的德性践履。
相比于新加坡,朱子学在越南的流传是具有相当广度的。秦汉时期,儒学伴随中国移民迁入越南而开始在越南传播(自秦、汉始至五代末,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曾为中国的郡县),越南的儒学已在越南存在了上千年,而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也从南宋末年(13世纪中叶)就已开始③,并在黎朝(1428—1788)到阮朝(1802—1945)的前期达到高峰,成为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在越南思想史上,曾出现了黎文休(1230—1322)、朱文安(1292—1370)、黎贵惇(1726—1784)等从事朱子思想研究的儒者④,并有一系列朱子学研究论著问世①。遗憾的是,朱子学在越南始终没有像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那样得到深化和细化。当代越南从总体上来说,也没有十分突出的朱子学研究成果(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越南的儒学研究成果,毕竟,越南拥有西贡文科大学、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人文与社科大学、汉喃研究院等众多研究机构,以及一大批从事儒学研究的当代学者,如陈廷厚、潘玉、武挑,等等)。管见所及,当代越南尚无朱子学研究专著问世。从越南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先秦儒家及越南儒学发展史上②。
附注
①据陈荣捷的考证,欧美人士关注朱子学的初衷乃是通过研究朱子及其他理学思想中的“天”之含义来解决西方传教士们就如何用中文翻译God一词而产生的争论(参见Wing-tsitChan. “The Study of Chu His in the West”.Journal ofAsian Studies.Vol.XXXV.No.4:555)。但北美学界对朱子的真正关注是以对朱子典籍的著译为开端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于1849年在自己创办的《中国丛报》上选译了《朱子全书》中关于宇宙、天、地、人和鸟兽等的论述,这是美国学界最早的对朱子文本的翻译。参见E.C.Bridgeman.“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heaven, earth, man, beasts, etc.”, Chinese Repository, VolumeXVⅢ,1849∶342-347.
①黄俊杰曾有一文《战后美国汉学界的儒家思想研究(1950—1980):研究方法及其问题》,讨论的是战后美国汉学界儒学研究状况,并选取了一些当代美国汉学界的代表作作为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样本(参见黄俊杰《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426页)。但这篇文章并不是专论朱子学方法论的。
②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年版。
①徐宏兴主编:《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明德出版社1996—1999年版。
③第一一三册,东京:汲古书院1991、1994、1998年版。
④汤浅的日译本被收入《中国文明选》第4、第5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2、1974年版。
⑤《孔子全书》全十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99—2006年版。
⑥东京:白帝社1988年版。
⑦《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16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92年版。
①《中国的古典》,东京:讲谈社1986年版。
②《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11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9年版。
③《人与文化丛书》第19卷,东京:人と文化社1996年版。
④《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84年版。
⑤《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2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版。
⑥《汲古选书》第14卷,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版。
⑦《东洋古典学研究》第20集,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2005年版。
⑧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7、294、300、301、311页。
⑨ Wm.Theodore de Bary, Wing-tsit Chan, Burton Watson(eds.) .Source of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⑩Ibid.:534—557.
⑪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本书的中译本在1993年由杨儒宾、吴有能等在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
①Wing-tsit Chan,Reflections on ThingsatHand:TheNeo-CoNFuciAn AnTH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②陈荣捷对《近思录》的评注内容经过增补修订,于1992年单独出版为一本专著《近思录详注集评》(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这本书的中文简体版在2007年问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④Gardner,Learningtobe a Sage:Selections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Master Chu,Arranged Topi-cal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10—81.
⑤Ho Kien Fou:Hsien hsien,1906∶171—194;2nd edition,1930∶187—197。戴遂良选译了《朱子全书》所采《朱子语类》中的理气、阴阳、性命等62条目。
①Bruce将他译注的《朱子全书》第42—48章独立成书,名曰The Philosophy ofHumanNa-ture(London:Probsthain,1922)。
②L'Ideée de DieuchezMalebranche et l' idée de li chezTchou Hi.Paris:Librairie PhilosohiqueJ.Vrin,1942.
③Dschu Hsi,Djinsilu,die sunkonfuzianische Summa mitdem Kommentar des Yd Tsai.Tokyo:Sophia University,1953,第二、三编。
④东京:日光书院1949年版。该译著的修订本被收入《世界文学大系》第69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版。
⑤收录于《新订中国古典选》第1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6年版。
⑥《新订中国古典选》第4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7年版。
⑦赤冢忠的译本收录于《新释汉文大系》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67年版。金谷治的《大学·中庸》收录于《世界文学大系》第69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版。后经增补,收入筑摩书房的《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18卷,1971年版。俣野太郎的《大学·中庸》收录于《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8年版。
⑧《新订中国古典选》第4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7年版。
①比如,岛田在解说《大学》时,论及了王阳明的学说,以比较朱子的学说;而在对《中庸》进行注释时,则特别又参考了日本儒者太田锦城的《中庸原解》、佐藤一斋的《中庸栏外书》等。
②《大学译注》与《中庸译注》以唐代石经《礼记》为底本。
③《大学章句译注》与《中庸章句序译注》依据的是吴志忠的嘉庆刊本《四书集注》。
④参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280页。
⑤汤浅的日译本被收入《中国文明选》第4、第5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2、1974年版。市川的日译本被收入《新释汉文大系》第37卷,东京:明治书院1975年版。
⑥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版。秋月的译本还参考了日本儒者中村惕斋的《近思录示蒙句解》,可惜的是,这一译本现已绝版。
⑦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
①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②陈荣捷另撰文数篇,专从史学角度进行朱子研究。如,“Chu His's Completion of Neo-Confucianism”,Francoise Aubin(ed.).Sung Studies,inMemoriam Etienne Balazs,2d,ser.I.1973∶59—90。囿于篇幅,本文不另作详细介绍。
③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④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
①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本书的英译改订版为Wing-tsit Chan,Chu Hsi:NewStudi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
②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6。
③Wing-tsit Chan.Chu His and Neo-Confucianis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6∶12。
④Thesis(Ph.D.).Stanford University,1960
⑤In:Arthur Wright,Denis Twitchett(eds.).Confucian Personaliti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62—188。
①In:John Haeger(ed.) . Crisisand ProsperityinSung China.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1975∶163—198.
②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78:127—148.
③参见Wing-tsit Chan. “The Study of Chu His in the West” .Journal ofAsianStudies.Vol.XXXV.No.4∶568,572。在近期的研究工作中,谢康伦似乎将关注点扩展到了对朱子历史思想的研究。参见Conrad Schirokauer, “Chu Hsi's Sense of History”In:Ed.Robert Hymes,Conrad Schirokauer(eds.) .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to State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193-220.
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⑤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卷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0—218、238—239页。
①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 Press,1992.
②本书的英文版于1992年出版之后,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本书的中文版问世,同样受到海峡两岸的广泛重视。田浩在综合海内外学者对此书的意见的基础上,于2009年9月在该书的中文增订版中新增了“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回应学界同仁对他在书中“过度强调朱子领导道学的企图”的质疑。另外,田浩还撰文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对当代儒学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作用做了探讨。这些新增内容都收录于本书2011年的版本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Tillmman,ConfucianDiscourseand ChuHsi Ascendanc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133-144,235-250.
④Tillman, Confucian Discourseand ChuHsi's Ascendanc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251-263.
①东京:创文社2004年版。
②《东方学报》(京都)第44、第48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3、1975年版。后于2001年被收入《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
③《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1988年版。
④《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2002年版。
⑤诸桥辙次、安冈正笃监修,阿倍吉雄、市川安司、冈田武彦等任编集委员,东京:明德出版社1974—1983年版。
⑥京都朱子学共同研究班分两期,第一期名为“朱子研究”,为期6年(1970—1975);第二期名为“《朱子语类》研究”,为期两年(1975—1976)。研究班的成员们主要是京都大学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大家相约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并从各自的专业领域提供研究朱子的新视角。这两期研究班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田中谦二的《朱子弟子师事年考》便是其中之一。
①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4、303—304页。
①参见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宁天平译,《中国哲学》第7辑,第146—158页;《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と現状》“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卷,第328—329页,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8月版;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历史学研究》第421号,第28—34页、27页,东京:青木书店1975年版。
②宇野哲人著有《支那哲学の研究》(东京:大同馆1920年版)以及《二程子の哲学》(收录于:井上哲次郎编《哲学丛书》第一卷第三集,东京:集文阁1900年版;后于1920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东京:大同馆)。他的译著《四书讲义:大学》(东京:大同馆1916年版。东京:讲谈社1983年新版)、《四书讲义:中庸》(东京:大同馆1918年版。东京:讲谈社1983年新版)以及《论语新释》(东京:弘道馆1929年版。东京:讲谈社1980年1月新版)等书籍曾多次重版,至今仍拥有广泛读者,影响巨大。
③东京:宝文馆1924年版。
④东京:宝文馆1954年版。中译本为马福辰译,《中国近世儒学史》(全二册),收录于“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7年4月。
⑤《朱子的哲学》, 《世界哲学大系》,东京:圣山阁1926年版; 《朱子的实践哲学》(1937);《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年版。这本书是后藤的遗稿,由其弟子整理出版。
⑥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
⑦东京:春秋社1969年3月版(1979年改订本)
⑧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
①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4;278—279页。
②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
③垣内所说的广义“心学”是与阳明学的狭义“心学”相对的。称朱子学为“心学”意在表明心的问题(或者说心与理的异同分合和相互关系)是朱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而阳明的狭义心学则主张心即是性。
④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⑤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再版。
⑥京都:同朋舍1981年版。
①东京:研文出版1999年版。
②据记载,安田曾通读朱子文集,并将《朱子语类》翻为日文。参见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宁天平译,《中国哲学》第7辑,第146—1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③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②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③陈荣捷:《朱学论集》,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④陈荣捷:《朱学论集》,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页。
⑤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① Munro,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192-232.
② Munro,Images ofHumanNature:A Sung Portra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18-19,28,155-191.
③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④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⑤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①这是由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东亚开创的传教策略,通过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方式,拉近在东亚儒学圈中生活的民众与传教士之间的心理距离,方便传教。这一策略后来被美国的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和发展。
②这一讨论在17世纪到18世纪初就已开始。当时以利玛窦为首的教士们主张,儒家所言的“天”和“上帝”即是天主教所说的“天主”。而以龙华民(Longobardi)神父为首的教士们则以《性理大全》为据,认为儒家并没有真正的作为人格神的God的概念。18世纪初,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著书专论朱子及其门人与基督教哲学家关于上帝的存在和性质之间的区别,释朱子及其门人为无神论者。至此,关于朱子神学观的讨论正式开始。
③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BookⅡ):History ofthe Scientif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412、453-493、510、542、558-559、579.
① In:Journal oftheNorthChina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49,1918∶1 1 1-127.
② London:Probsthain,1923.
③ Hamburg:Friederichen,de Gruyter and Co.,1938.
④ 参见萨金静的博士论文TschouHi contre le bouddhisme(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 955) 和论文 “Les Debats personnels de Tchou Hi en matiere de methodologie” .In:Journal Asia-tique,253.1955:213—228。
①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这几位学者的朱子学比较研究的诚意和成果。只是因为他们的比较研究着意于在短小篇幅内(只是论文而不是专著)从速比较朱子思想与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异同,虽可能为朱子学研究提供某种西方新视角,但不免将西方概念和思想派别强加于朱子。参见Bruce对朱子的“太极”与斯宾诺莎的“上帝”特性的比较:ChuHsiandHisMasters.London:Probsthain,1923∶148,241;Graf神父对朱子与斯宾诺莎一元论的比较以及对朱子的神学观与托马斯·阿奎那的有神论的比较:DschuHsi,Djin silu,die sunkonfuzianische Summamitdem Kommen-tar des YaTsai,Tokyo:Sophia University,1953∶278-297;以及Needham对朱子与怀特海、莱布尼茨机械论的比较:Scienceand CivilizationinChina(BookII):History o旷the Scientific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458、474、478、496-505 。
②Harvard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Volume l,1936∶109-127.
③ 如Paul E.Callahan. “Chu His and St.Thomas:A Comparison”.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on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Papers on China, Volume 4, 1950:1-23.
④对陈荣捷的这几本重要的朱子学考证著作的介绍,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声韵训诂的方法”。
① 如, Andrew J.Dell'olio. “Zhu Xi and Thomas Aquina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 Self-Culti-vation”.Proceedings of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77(2003)∶235-246.又如,Kenneth Dorter, “Metaphysics and Morality in Neo-Confucianism and Greece:Zhu Xi, Plato, Aristot-le,and Plotinus” .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8.3(Sep 2009):255-276.
② 比较著名的有成中英(Cheng Chung-Ying)的论文“Ultimate origin,Ultimate Reality,and the Human Condition:Leibniz,Whitehead,and Zhu Xi”.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29.1(Mar2002):93-118.以及黄勇的一系列论文“Zhu Xi on Ren(Humanity)and Love:A Neo-ConfucianWay out of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Impasse”.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23.2(Jun 1996):213-235;“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84.4(Oct 2010):651-692;“Two Dilemmas in Virtue Eth-ics and How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voids Them”.Journal ofPhilosophical Research36(201 1):247-281.
③ New York:SUNY Press,1998.
④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⑤参见伍安祖《北美学界朱熹研究近况》,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注释,诠释,还是创构?》,刘笑敢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273页。
① Berthrong, 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ChuHsi,Whitehead, andNeville, NewYork:SUNY Press 1998:74-79,111-141.
② Ching,Julia,The Religious Thought ofChu Hs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32-53、59-60、67、81、94、123-236、212-213、228.
③ Ching,Julia,The Religious ThoughtofChuHs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44-47、115-122、195-196、210-211.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9—147页。
②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
③柏: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版。
④京都:平乐寺书店1963年版。
⑤东京:木耳社1983年版。
①楠本正继:《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东京广池学园出版社1962年版,第218—277页。
②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京都平乐寺书店1963年版,第194—369页。
③周全华,林珍妮译:《朱子学刊》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⑤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⑥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⑦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①笔者对这种普世价值的可行性存疑。以狄百瑞探求儒家自由精神的普世性为例。狄百瑞基本上是以朱熹等宋代儒者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来探求中国自由精神的,但宋儒谔谔之士的风骨是与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余英时就曾指出,宋代是“士”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但这是一个历史的例外,也就是说,宋代的政治气氛是不怎么具有普遍意义的。
② Wm.Theodore de Bary.Neo-Confucian Orthodoxyand theLearning oftheMind-and-Hear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2—17.这与日本朱子学专家垣内景子在《朱子思想的结构的研究》中的主张有类似之处。只是垣内的研究似乎并不具有狄百瑞著作中充溢的“为己之学”精神。
③广岛: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54、1955年版。
④名古屋:采华书林1975年版。
⑤台北:广文书局,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1977年版。
⑥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年版。
⑦东京:东丰书店1980年版。
①此文初载于東洋の思想と宗教,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1996年版,第26—39页,后被收录于土田的专著《道学の形成》中。
②《创文》,东京:创文社2003年版,第21—26页。
③参见安田二郎《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
④参见早坂俊广《“宋明思想”研究的現状与課題,中国——社会与文化》,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4年版,第401页。
① Hans-Georg Gadamer.TruthandMethod.Joel Weinsheimer&Donald Marshall(trans.).NewYork:Continuum,1994:265—379.
②周全华,林珍妮译:《朱子学刊》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年版。
④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幸德秋水、堺利彦、福本和夫、櫛田民藏、河上肇、户坂润、三木清、古在由重等,组织了“唯物论研究会”,翻译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作品,《马克思斯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的日译本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①20世纪60—70年代,以下列现象为标志,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第一,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林立,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代表学派有“宇野经济学”、“大冢史学”、“望月史学”、“《现代的理论》学派”、“市民社会派”等。第二,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的论争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有:围绕《巴黎手稿》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围绕《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论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中期马克思论争”和“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围绕法语版《资本论》的“个体所有制”论争;第三,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新问题,如黑格尔左派和早期马克思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史像理论”问题等。
②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
③东京:未来社1967年版。
④“丸山政治学”是指日本著名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政治学思想。丸山政治学承继了德国黑格尔思潮,并融入韦伯、舒兹、曼海姆等德国知识社会学家的理论。丸山的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版)在日本影响甚广,并于2000年被王中江翻译为中文,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① “Studying Confucian and Comparative Ethics”.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Vol.36, No.32009:455-478.
②文中所说的韩国朱子学研究指的是朝鲜半岛(包括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的朱子学研究。
③《高丽史》列传卷十八。
④《高丽史》列传卷十八。
①《高丽史》列传卷十九。
②《高丽史》列传卷二十。
③《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八。
①《高丽史》列传卷二十八。
②《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③《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④《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⑤《高丽史》列传卷三十。
⑥《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
①林鲁直:《退溪学派的〈武夷棹歌〉受容和陶山九曲》。
①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形成于16世纪,前者是主理派,尊奉李退溪的思想体系,后者是主气派,尊奉李栗谷的思想体系。
②参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第84页;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23—324页。
③参见《毅庵集·散言》,卷二十七,杂著,乙未十一月。
①参见《毅庵集·散言》卷二十七。
②参见《秋潭别集》卷三,第36—37页。
③参见《秋潭别集》卷二,第7页。
④《秋潭别集》卷三,第2页。
⑤开化论派的主要代表是金玉均(1851—1894)、徐载弼(1866—1951)、朴泳孝(1861—1939)。
①李光麟:《旧韩末新学与旧学之论争》,《韩国开化思想研究》,肃兰市:潮阁1992年版,第205—206页。
②这也被认为是韩国现代新儒家的理念。参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第87页。
③参见《朴殷植全书》下卷,第44—47页。
①以日本学者高桥亨为代表。他从殖民史观出发,著有《朝鲜儒学史大纲》(1925)和《在朝鲜儒学史的主理派与主气派的发展》(1929)二书,宣扬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正当性。
①三省文化财团1972年版。
②参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版,第97页。
③均收录于《李相殷先生全集》。
④载《亚细亚研究》,高丽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3页。
⑤李相殷:《儒学与韩国思想》,《李相殷先生全集》(韩国哲学Ⅱ),第121页。
①参见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第45—47页。
②延世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③成均馆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75年版。
④载《韩国思想大系》,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6年版,第80—91页。
⑤槿域书斋1983年版。
⑥傅济功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⑦玄岩社1980年版
① Chan Wing-tsit ed.,ChuHsiandNeo-Confucianis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570-583。本文讨论朝鲜李朝朱子学史上最大的两大争论之一——人、物之性是否相同(另一个争论是著名的四端七情之辩),肇始于李朝大儒韩元震与李东之间的论辩。
②乙酉文化社1984年版。
③国际退溪学会2000年版。本书介绍了韩国性理学大儒李退溪的生平和哲学(包括理气论、心性论、敬学)、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当代意义,等等。
④载《世宗朝文化研究》,博英社1982年版。
⑤载《韩国思想》,烈音社1984年版。
⑥博英社1984年版
⑦高丽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⑧杨秀枝译,《韩国学报》,1986年第6期,第169—188页。
⑨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版
⑩汉城:玄音社1986年版。
⑪《杭州师范大学学报3.2》(2008),第45—47页。
⑫韩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⑬首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是关于高丽末期大儒郑道传(号三峰,1342—1398)的生平、著述、思想的综合研究成果。
⑭这几篇均是第九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参见高令印《国际朱子学研究的新动向》,邹永贤主编:《朱子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①刘李胜、李民、孙尚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①参见梁承武《韩国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第48页。
②这三本集注均是由成百晓翻译、民族文化研究会出版的。
③任敏赫翻译。
④赵敦相、崔载铉翻译。
⑤许铎、李尧圣译注,清溪出版社出版。
⑥弘益出版社。
⑦ Yung Sik Kim.TheNaturalPhilosophy ofChiHsi(1 130—1200).Philadelphia: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2000.
⑧Ibid..
①金永植:《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15—241页。
①具体情况参见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I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6:33-57.
②参见冯增铨《儒学在新加坡》,载《孔子研究》,1986年版。转引自高令印《朱子学在新加坡和泰国的传播和影响》,邹永贤主编:《朱子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③参见李焯然《儒家思想与新加坡》,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第180页。
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
①新竹《清华学报》新23卷,1993年第4期,第429—448页。
②这是龚道运在1987年12月初在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的学术演讲。
③陈太宗曾按照朱子学理论来改造尚不成规范的礼仪;还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设立国学院,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朱子学和“四书”“六经”,传播朱子学。之后,朱子学逐渐成为官学。明成祖朱棣时期,在越南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并广办学校,颁赐《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等书籍供越南士子学习,加速了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参见李世财、杨国学《朱子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建构特征比较》,《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页。
④朱文安著有《四书说约》,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介绍了《四书》的内容,这是朱子学传入越南的最早证据。黎贵惇受朱子理气论的影响,在《芸台类语》中将《理气》篇列为首篇。但有学者研究指出,《芸台类语·理气》篇中并未严格遵循朱子强调的儒释道之分,由此可知,《理气》篇虽涉及朱子思想,但并不以其为宗。相反,《理气》篇的论述较接近气化宇宙论的实用观点。参见蔡振丰:《黎文敔〈周易究原〉与其儒学解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2年9月第2期,第104—105页。
①黎显宗景兴年间(1740—1786),范贵适取材于程颐《易经序》、程颢《易经序》、朱熹的《图说》及《朱子五讚》、《易说纲领》、《朱子筮仪》等,撰写成《易经大全节要演义》。黎朝时期的问答体科举文集《周易策文略集》(汉文书),附载有《易序》《程子序》和朱熹《周易图说》。黎朝大儒黎贵惇著《四书约解》的内容,主要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另据记载,越南学者裴辉碧撰写的《性理节要》,又名《性理大全节要》(汉文书),为朱熹《性理》一书的概要,于绍治二年(1842)、三年、四年连续印行。《性理略集》(汉文书),为朱熹《性理》一书的评注本。绍治三年(1843)壬寅科进士潘廷扬的《行吟歌词诗奏》文集(汉文书)刊印,该书收集有《朱子家训演音》跋。成泰六年(1894),《朱子家政》重印于慈廉县上葛社三圣庙。该书后附载《女训要言》论及女子四德。《名诗合撰》(汉文书)系诗文集。此书包括五部分,其中第四部分为《朱子家训》。《朱子小学略编》(汉文书)为蒙学教科书《朱子小学全书》的简编,刊印于成泰甲午年(1894),该书总论、题词、序文及书中主要内容採自朱熹,陈选集注,桂山阮劝撰再版序文。《小学句读》(汉文书)为蒙学教科书,内容从《论语》《孟子》《朱子语录》等书中摘出的若干短句而成。《筮仪演义》(喃文书),题朱子撰,为《筮仪》的喃译本,每句汉文原文后为喃译。从以上介绍可知,除了越南官方大量印行朱熹的“四书”外,阮朝还先后出现过一些用汉字或者喃字翻译注释、阐发朱熹的其他著作。可见,当时朱熹的著作在越南的流传相当广泛。参见张品端《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1.1期,第81—86页。
②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是,陈重金撰写的《儒教》(1928),这是20世纪初最为系统地向越南读者介绍儒教知识的读物;潘佩珠的《孔学灯》(1957);阮才书主编的《越南思想史》(1994);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学者编纂的《越南文学历史》(1988);陈廷厚的儒学研究作品《从传统到现代》 (1992;1994);潘玉的《越南文化本色》(1998);武挑的《儒教及其在越南的发展》(1997);潘大尹主编的《关于越南儒教的若干问题》(1998),等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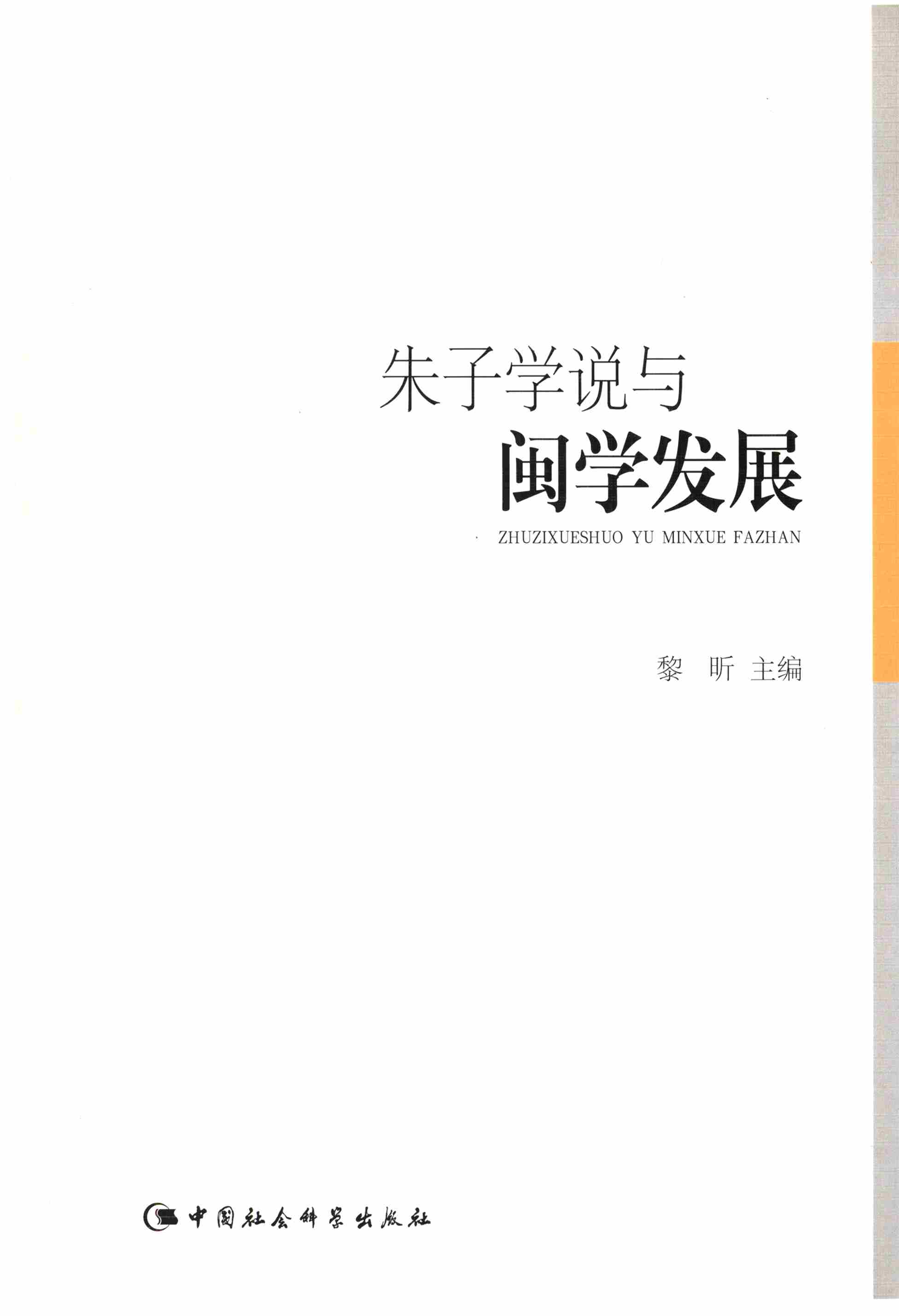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八章,主要包括福建历史文化发展与闽学的产生、朱子学说与闽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传承、朱子学说与闽学思想的基本内核、朱子学说与闽学的社会教化论、朱子学说与闽学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等内容。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