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733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我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5 |
| 页码: | 149-173 |
| 摘要: | 本章主要探讨了我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文章概述了20世纪以前和以后,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对朱子学的研究情况,分析了不同地区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特点和贡献。 |
| 关键词: | 朱熹 闽学 研究 |
内容
钱穆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①钱穆先生客观地概括了朱子及其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从古代学术门类来看,朱子学不仅触及理学、经学、史学、子学、小学等领域,而且在各领域都是成就卓著,堪称集大成者。从现代学科分类角度看,朱子学涉及哲学、文献学、史学、文学、伦理学、美学等多种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有涉及,而且朱子在各个现代学科领域当中,依然是古代思想家当中的佼佼者。朱子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朱子学在朱子去世后不久,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朱子的著述渐渐成为后世士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子学在科考废除之前毫无疑问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从政治意义出发,朱子学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思想家讨论、批判、研究的对象。然而,鉴于朱子在各领域的成就,后世思想家很难从总体上超越他,转而只能在某一特定领域朝着“窄而深”的方向发展。
依照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内朱子学研究可以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为界,大致划分为两阶段: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20世纪后中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总结20世纪前的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可以归纳为儒学内部对朱子学的修正。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子距今仅八百年,后人之阐发容未能尽。而反朱攻朱者,多不出于百家众流,而转多出于儒学之同门。”“诤朱攻朱,其说亦全从朱子学说中来。”①综观20世纪以后国内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则鲜有纯粹从儒学内部阐发朱子学的现象,而是普遍从西方哲学、史学等现代学科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朱子学涵盖甚广,既包括了朱熹本人及其弟子后学的思想学说,也包括了深受朱子学影响的“东亚文化圈”之中的思想家对朱子学说的阐释,这就意味着朱子学研究综述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绝非本章所能囊括。因此,本章的“朱子学”仅限于后人对朱子本人学说的阐发和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
20世纪以前,因为统治者推崇的缘故,一方面朱子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既控制着庙堂之上的思想倾向,也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当中;另一方面朱子学作为涉及理气、心性等本体功夫论的学说体系,深深吸引着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朱子学说做出自己的解读。于是“述朱阐朱”成为“中国学术上一大争议”②,这些“学术争议”大体可依对待朱子学的态度分为两方面:一是朱门后学以及官方对朱子学的继承和阐发;二是陆王心学、气本论、事功学派、汉学等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发展。具体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 朱门后学对朱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与陆王心学相比,朱门弟子众多,再加上朱学普遍重视读经注经、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因此朱学在朱子去世后一直连绵不绝,即便是在明中期阳明学兴起之后、清代汉学盛行之时,朱子学派也从未中断。但是由于朱子对理学的义理阐发可以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朱门后学对朱子理学的新发展微乎其微,基本停留在对理气、心性、格致等传统理学的阐释上;与朱子理学相较,朱子对《四书》学、《五经》学的注释、解读却为后学留下了一定发展空间。于是朱子弟子及其后学主要是在对朱子四书学、五经学、小学等著述的阐释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在朱子的亲炙弟子中,陈淳著有《四书性理字义》和《严陵讲义》。前者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二十五个范畴,是后世理解《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后者则全面继承朱子理学思想,是后世理解朱子理学范畴的重要参考书。黄榦继承了朱子《礼》学思想,与杨复一起续补修成朱子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同时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继承了朱子对《五经》《四书》的基本观点。蔡元定和蔡沈父子对朱子的象数易作了进一步发展,蔡元定著有《皇极经世指要》,概括了邵雍的思想,蔡沈著有《洪范皇极》,发展了理学象数学。同时,蔡沈还依照朱子的嘱托,以“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为宗旨,完成《书集传》,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尚书》思想。朱子向来看重小学,亲自编纂蒙学读物,在其弟子当中,程端蒙著有《性理字训》,朱子认为:“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①程端蒙还同董铢合作制定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对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作了总体规划。由于朱门弟子一向有重视读书著述的传统,所以朱门弟子对《四书》、《五经》、小学、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而像《北溪字义》《书集传》《性理字训》等朱学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南宋朱子后学一方面为朱子学的传播及其上升为官学做出努力,以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另一方面则继续阐发朱子理学、经学等思想,为朱子学传承至元明奠定基础,以黄震、“金华四先生”为代表。真德秀早年从游于朱子弟子詹体仁,他所著《大学衍义》是对朱子《大学章句》的阐释,深得当时乃至后世皇帝的重视。魏了翁著有《九经要义》,主要是注疏释文,对朱子的理学思想鲜有发展。真德秀、魏了翁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推动了朱子学由“伪学”最终转变为官学。黄震是朱子弟子辅广的三传弟子,他的《黄氏日抄》是读经史子集的札记,其中不乏有对程朱思想的批评和修正。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均属黄榦后学。何基从学于黄榦,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莫不以朱学为依归。王柏从学于何基,金履祥从学于王柏,许谦从学于金履祥,他们在五经、四书、理学等方面都有大量著述流传后世。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柏、金履祥继承了朱子“疑经”的传统,王柏著有《诗疑》《书疑》《大学沿革后论》《中庸论》,金履祥著有《尚书注》《论孟集注考证》等,对传统四书五经,乃至朱子著作和学说都提出很多疑问。金华朱学直接影响到元代乃至明初理学。
元代许衡、刘因、吴澄等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许衡在元朝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这与其不遗余力地传播朱子学、积极推动《四书集注》在延祐年间定为科场程式有关。许衡虽继承朱学,但并没有严守朱学门户,其心性论游离于朱子“穷理以明心”和陆象山“明心以穷理”之间。刘因极力推崇朱子,认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①。他对理学和经学、史学的关系上看法独到,认为理学本于六经,“古无经史之分”,即《诗》《书》《春秋》等经就是史,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对经学、理学、史学的看法。吴澄拜饶鲁弟子程若庸为师,饶鲁则是黄榦的高弟。吴澄以接续朱子为己任,著有《五经纂言》,发展了朱子学。其中,吴澄在三礼上的成就深受后人肯定。在三礼上,吴澄依朱子的端绪和规模,“以《仪礼》为纲”,“重加伦纪”,全祖望谓“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由之,用功最勤”②。许衡与吴澄都以朱学为标帜,但他们由朱学的心外格物,移到陆学的直求本心,是宋代程朱理学发展为明代王学的过渡。
明朝中后期几乎是阳明心学的天下,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明朝初期,代表人物有宋濂、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宋濂传承了金华朱学,因其喜援佛入儒,认为儒佛“本一”,所以全祖望称之为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宋濂认为,吾心为“天下最大”,识心明心是“不假外求”的内向冥悟,体现出元末明初理学调和朱陆的倾向。曹端被清人认为“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③。曹端发展了朱子理气论,他反对朱子把太极与动静、理与气看成二物,认为太极自能动静,因此不同意朱子所谓理气如人之乘马的比喻。薛瑄发挥朱子“理气相即”的观点,抛弃了所谓“理先气后”的提法,在曹端提出的“理气未尝有间隙”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理气关系。与薛瑄偏于下学相比,吴与弼则侧重于“寻向上工夫”。吴与弼主张静观修养论。其弟子分为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①,这一派观点与王阳明心学相似;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②,这一派仍有朱子学之风。待到阳明心学昌行,朱子学作为官学,已是徒具形式,思想上毫无创见。当王学末流弊端逐渐显露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重新推崇朱学,遵奉“性即理”“居敬穷理”“格物穷理”,以朱学批判佛学和王学,但对朱子学体系并无明显发展。
明末清初朱子学仍有信奉者,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为代表,对朱子学说以维护信奉为主,在学说创见上并无太大功绩。陆世仪否认理游离于事物之外,反对离气质而言性,强调“人性之善正在于气质”。他还发展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说。陆陇其极力尊崇朱子学,贬抑阳明学。他继承了朱子“理之流行”说和“居敬穷理”论。李光地著作宏丰,遍及四书、五经。他虽学宗程朱,但并未全盘肯定朱子学。其理学的最高范畴是“性”,而不是“理”或“心”,主张“性为本气为具”的性气观。李光地奉命编纂《性理精义》等大量理学著作,对朱子学著作的整理和传播颇有贡献。
二 官方对朱子学的阐释和利用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庆元至嘉定的二十余年间,一直受到禁锢。后来在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极力提倡下,宋理宗逐渐确立理学为国是。元仁宗延祐年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标准,《四书》主朱子的《四书集注》,《易》主《程氏易传》,《书》主蔡沈《书集传》,《诗》主朱子《诗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于是,朱子学在元朝通过科考正式成为官学。
明清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经传、集注以及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出版,其目的并不在于发明理学义理,而在于以钦定形式确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使之更好为科举考试服务,进而为他们的统治服务。明永乐十三年,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作为教授生徒、科举考试的准绳。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周易大全》依据《伊川易传》及朱子《易本义》,《书传大全》依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子《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主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乃朱子弟子,陈澔之父大猷师饶鲁,饶鲁师黄榦。所以《五经大全》所据传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四书大全》是对《四书集注》的进一步扩充,其中所引用“先儒”之说,有106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程朱学派中人,以朱子弟子及后学为主。《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也十分明显,卷首所列“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程朱学派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所收先儒著作,或为朱子所注,或为朱子所作,或为朱子门人所作。其中语录的编排体例完全模仿《朱子语类》的门目。
清朝初年,在康熙帝推动下,李光地等人奉命编纂了《性理精义》。《性理精义》是《性理大全》的精简本,主要选取宋元时期四十五位理学家论学、论性命、论理气、论治道等若干言论而成,其主要思想、观点、材料都在《性理大全》的范围内。除《性理精义》之外,李光地奉命编订的性理之书还有:编《朱子语类四纂》五卷(康熙三十四年);《二程遗书纂》二卷(康熙三十五年);《朱子礼纂》五卷(康熙四十六年);奉命与熊赐履等编《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等。《朱子全书》是从《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类编次”而成。在李光地编纂的系列著述中,《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费力最大、影响最大,可以说,这二书代表了清朝官方对朱子学的基本理解,因为不仅它们的编纂工作是在康熙直接主持下进行的,而且康熙亲自审订其宗旨、体例、选材、编次以至校刊,并为之作序。直到1905年,《大全》《精义》等官学著述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才彻底告别了过去一统天下的时代。朱子学也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新文化运动而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殿堂,在近现代学术界常常被看作中国学术思想史当中的一个学派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三 陆王心学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吸收
陆王学派与朱学同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所以陆王学派对朱学的批判或融合仍属于传统理学内部的讨论。由于陆九渊不像朱子那样重视著书立说,所以陆九渊去世后,其弟子对陆学的认识已经很模糊,以至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朱学思想。陆九渊的弟子包扬,“及象山卒,即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槐堂诸儒学案》)包扬之子包恢,史称“少得朱陆渊源之学”。包恢弟子龚霆松则有“朱陆忠臣”之称,著有《四书朱陆会同注释》。南宋陆学的主要人物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是同乡,被称为“甬上四学者”,其中舒璘、沈焕也都表现出折中朱陆的倾向。舒璘曾与朱子书信往来,一度对朱子的致学方法及其推崇的“二图”(先天图,太极图)提出质疑。沈焕对朱子一直表示尊敬,丝毫没有朱陆对立的痕迹。
明代陈献章和湛若水继承并发展了吴与弼的思想,他们都不否认朱学,对朱陆基本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王阳明心学则是源于对朱子理学的改造。王阳明曾经“泛滥辞章”“遍读考亭遗书”,致力朱子学,年轻时曾亲身实践朱子的格物穷理说,一连七天静坐试图“格”竹子之理,最终失败。后来王阳明逐渐放弃了朱子学,提出了与朱子的天理论、格物说、知行说等对立的心学体系。王阳明反对朱子的“性即理”,主张“心外无理”;反对朱子的“知先行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朱子对“格物”的解释,提出以《尚书》中的“格其非心”为例,“格物”的“格”,不能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但阳明心学依然沿用朱子学的很多理学范畴,比如他最著名的“致良知”说仍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容的。
明末清初,王学末流弊端显现,于是心学内部出现了借鉴朱子理学修正心学的倾向。刘宗周提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把朱子的“无一毫人欲之私”的“第一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联系起来,希望能够实现“克去人欲之私”的目的。黄宗羲也试图通过“道问学”以成就“尊德性”,一改不重读书著述的心学传统,提倡读书,注重研究经史和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这明显带有朱学的特点。不过黄宗羲的基本立场仍是心学,所以在其《宋元学案》中评价朱陆时明显表现出右陆左朱。
无论官学的支持利用还是心学的批判无不是从遵奉宋明理学这个大前提出发的,而以下三种对朱子学的批判则着眼于批判整个宋明理学——包括朱学、陆学、王学。这是因为,到了明末清初,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经历了长期发展之后,迟迟没有产生新理论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程朱陆王展开批判,以期创立一种能够改变甚至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宋明理学。
四 从气本论角度出发批判和发展朱子学
在明朝中后期王学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从气本论角度批判朱子理学的理学家,以罗钦顺、王廷相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以张载的气本论为依据,对朱子的理气论进行了检讨,提出了自己的理气说。黄宗羲评价罗钦顺:“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又说:“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罗钦顺认为气是最根本者,理只是气之条理,理在气中而非与气对立,这与朱子理先气后思想明显不同。王廷相在其《慎言》中表达了“气本”论。他认为并非气本于理,而是理根于气。他批评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说,提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的命题。他还将“性理”气化,批评程朱理学的“性即理”,否认存在先天的“德性之知”,由此也就否认了性善论。在修养论上,他既反对程朱的“体认天理”,又反对陆王的“讲求良知”,独以张载为宗。
在明末清初,王夫之继承张载的气本论,反对朱子将理与气二分,认为气是宇宙中根本,无气则无理。“理在气中,气无非理。”他认为理即秩序,且即气之秩序。在形上形下关系上,他认为形而下之“器”是根本,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所谓“天下惟器而已,道者器之道”。他认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他批判朱子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结论。
五 从实学出发对朱子学的批判
颜元、李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不仅对朱、陆、王进行批判,而且直接批评周、程、张、邵等理学开创者,认为理学家声言“明体达用”,其实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他们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其实源于佛老。颜李学派以陈亮的事功学作为出发点,他们常常讨论的话题有:理事、体用、动静、知行、形性、性习、道艺、义利等。他们反对“理在事上”“理气二本”,主张“理在事中”“理气一致”。他们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敬持敬的心性修养,注重实践,崇尚技艺,讲求功用。他们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肯定人欲的合理性。颜元著有《四存编》《朱子语类评》《四书正误》《习斋记余》等,内容均以批判朱子为主。严格说来,颜李学派与理学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在根本上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颜李学派反对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致用”的实学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之下理学日渐衰退的必然反动。
六 从汉学角度出发对朱子学的批判与发展
清代学术以汉学最为辉煌,是作为宋学的对立面出现的,顾炎武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顾炎武试图以经学家的见地来改造理学,朱子在他心中的形象,与其说是理学家,倒不如说是重视训诂、明于典章制度的经学家。顾炎武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对经学考辨精审。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的观点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转向。清代朴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疑经的传统,传统儒家经典无不遭到质疑、考辨。如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古文尚书》及其《孔安国传》为伪书,这发展了朱子疑《古文尚书》的观点。毛奇龄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专辨象数图书;胡渭的《易图明辨》,专辨《河图》《洛书》。由于“无极”“太极”《河图》《洛书》是“宋学”的根本,宋代理学家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所以毛奇龄、胡渭对图书的考辨无疑触及了宋代理学的基石。姚际恒著有《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毛奇龄著有《四书改错》,专门针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认为朱子注几于无一条不错。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这些著述无不继续发扬着朱子的疑经作风,只是他们大都以批判朱子的经学传注为目标。
汉学家在全力批判朱子经注时,并不意味着贬抑朱子。阎若璩曾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惠士奇尝手书楹联曰:“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可见他们虽尊汉但并不反宋。江永也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作《近思录集注》,对朱子著作进行阐释。陈澧著有《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并不排斥注疏,相反提倡读注。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批驳汉学,尊崇宋学。清儒除批判朱子著述外,又有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对朱子的生平进行考证,是以汉学路子研究朱子的典范。
总起来说,从朱门后学对朱子学的阐发至颜李学派对朱子学的批判,无不从朱子学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说、经学传注等方面入手的,他们述朱攻朱的出发点无不从“经世致用”的儒学角度出发,直到清代早期顾炎武、阎若璩等虽以考证方法治经但仍在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与理学家由格致诚正以求修齐治平的为学目标是一贯的。这种治学的目标和方式与近现代“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并不一致。随着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汉学家渐渐放弃了“致用”的幻想,而走向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治学路径。因而,梁启超先生说:“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①又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②这种“科学精神”已经接近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了。
第二节 20世纪后中国大陆对朱子学的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渐渐被西方学科分类所取代,于是,朱子学研究出现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划分,其中以哲学研究朱子学的成就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前朱子学研究方法多样,视野广阔,成就斐然,特别突出的是一些哲学家运用西方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和发展朱子学,进而提出新的哲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去看待和评介朱子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对朱子学基本持批判、否定态度,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乏善可陈。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环境日趋宽容开放,学者对朱子学的各种研究也逐渐能够秉持客观公允的基本立场,不仅对朱子学的哲学研究成果突出,而且从史学、文献学角度对朱子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辉煌的学术成果。以下将从哲学、史学、文献学及其他四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国内朱子学研究方法做一归纳。
一 哲学角度
大陆从哲学上研究朱子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冯友兰,他通过对朱子理学的深入剖析,创立新理学体系,从理论体系上发展了朱子学。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则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朱子学的某一方面进行归纳分析,向现代读者展示出异彩纷呈的朱子学。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估朱子学;以陈来为代表的学者专注于分析朱子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张立文为代表的学者着重于比较朱子学与其他学者或学派的异同;以蔡方鹿、朱汉民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西方解释学角度出发分析朱子学。
(一)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结合相关文献,深入剖析朱子理学,从而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冯友兰为代表。
冯友兰在抗战时期著成《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了新理学体系。所谓新理学就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所谓“接着”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的理学。一方面,冯友兰把朱子学的精髓转换为“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内在要素;另一方面,他又以哲学家的视域反观朱子学。冯友兰运用“以西释中”的框架对朱子学进行了诠释,他说:“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著力。”①冯友兰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朱子学当中的理、气、心、性等概念进行分析。在《新理学》中,他依照“新实在论”把理世界解释的真际世界,气世界解释为实际世界,认为理世界与气世界构成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朱子学进行重新评价,主要体现在建国后大陆编纂的《中国哲学史》之中,以任继愈、侯外庐、邱汉生、冯友兰等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自古存在唯物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从唯物、唯心角度评价朱子哲学的。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年版)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63年版)中,朱子都是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被批判的。侯外庐、邱汉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1987年版)也受到哲学史研究的影响,由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发展出“理学与反理学”的模式,继续表彰反理学的思想家,朱子学仍是作为唯心主义者受到批判。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1980年版)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四书集注》做了论述。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诠释框架,对朱子学做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道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朱子学既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也是后期道学的肯定阶段。他还说:“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②
另外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1981年版)、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影响。
(三)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基本兼采哲学范畴的分析与文献资料的考证的方法,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朱陆异同等问题的产生、演变做了深入的考辨和分析。陈荣捷认为此书“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特别提到陈来对理气先后的考证足以“补冯友兰等学者逻辑推究说之不足”①。
近年来有学者引入发生学的概念,对朱子学进行分析。2010年丁为祥发表《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在他看来,牟宗三、刘述先对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指其“哲学理论逻辑(所谓内在必然性、架构性)或思想谱系性的展开,与朱子本人的人生现实并不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于是他主张从朱子的生存心态、学术性格等主体性因素出发,对朱子思想进行发生学的解释,试图解答朱子的哲学视野、思想体系、历史影响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等问题。2012年丁为祥出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阐发。
(四)比较方法研究朱子学。
张立文的《朱熹与退溪思想之比较研究》(1995年版)将朱子与朝鲜的李退溪进行比较。又有不少学者常常将朱子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如冯友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等范畴来解释朱子的理气说,他认为朱子所谓“月印万川”与柏拉图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都是为了解释一与多的关系,朱子的修养方法,也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2011年刘光顺以《宇宙生成论的中西比较——以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例》为题对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比较。潘德荣则将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进行比较,他在《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中指出,朱子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视为经典解释的第一目标,施莱尔马赫则把揭示作者的原意视为解释的根本目的。
(五)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研究朱子理学和注经的关系,一方面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注经与创立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出中西解释学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从2000年出现延续至今,以蔡方鹿、朱汉民等为代表。
有的学者对朱子学的解释学进行归纳概括,如蔡方鹿分析了朱子经学、理学、哲学的关系,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学融合了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形成较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潘德荣在论文《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提出“理”是朱子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朱汉民则在论文《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中,指出朱子是运用“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刘笑敢以《论语集注》为例,提出“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概念,强调在一般的经典诠释中,有“两种定向”“两个标准”。朱熹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形式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何俊以《论语·学而》篇首章的四种诠释为例,论证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他认为朱熹以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归宿,融合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使宋代儒学在方法和思想两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①
二 采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借助于传记体等传统形式,对朱子的生平、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束景南、张立文、高令印等
束景南的《朱子大传》(1992)“是一部心态研究之书,是用传记体的形式研究道学文化心态的著作”②。作者采用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探讨朱子的一生与思想发展历程,所谓“文化还原”法是相对于那种“把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理‘过滤’为一般的哲学原理、人生信条与政治原则”的“古典”研究方法而言,它“是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念与政治追求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具体——可以称为活的文化还原法”③。另外,学界还有两部《朱熹评传》,全面阐述了朱子的生平与思想,一部是陈正夫、何植靖合著,一部是张立文所著。除梳理朱子的思想变化外,还有对朱子的活动、事迹的考证、分析。比如,高令印在1987年版的《朱熹事迹考》,是结合实地调查对朱子的主要事迹做考证。束景南在2001年出版的《朱熹年谱长编》对朱子一生中的重大的学术活动作了详细记述、按评。
三 从文献学角度,对朱子的著作及其文献学贡献进行考证与梳理,以陈来、束景南、白寿彝等为代表
由于朱子的著述宏丰,完成时间不详,所以有很多学者对朱子的相关著述的年代进行考证。1989年陈来出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是对朱子书信的年期作考订,陈荣捷评价此书道:“数量之多,考据之实,远出乎王懋竑《朱子年谱》与钱穆《朱子新学案》之上。”①陈来又有《朱熹观书诗小考》《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等论文对朱子相关著述做了考证。束景南在1991年出版的《朱熹佚文辑考》对朱子诗文、书信、著作、语录等的年限进行了考证。对朱子著作进行考证的论文还有:钦伟刚在2004年发表的《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考》、杨文森于2007年发表的《朱熹证伪古文尚书及序、传详考》、李永明于2008年发表《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赵振于2007年发表的《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除此之外,华东师大出版社对朱子著作进行整理出版,为现代朱子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在2010年,为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朱子著述宋刻集成》《朱子全书外编》《朱子全书》(修订版)三套图书。
除对朱子著述进行研究、整理之外,又有学者对朱子的文献学成就进行归纳总结。白寿彝在1933年出版的《朱熹辨伪书语》所辨书近五十种,体例是将《语类》和《文集》中关于朱子辨伪的资料列于所要考辨书籍之下。1987年,王余光和钱婉约发表《朱熹在辨伪学上的成就和影响》,1988年,孙钦善发表《朱熹与古文献学》都对朱子的文献学成就进行了梳理。相关主题的论文还有叶建华的《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1990),曾贻芬的《朱熹的注释和辨伪》(1993),华星白的《朱熹的古籍注释》,杨绪敏的《朱熹考辨古书真伪的成就、方法及影响》(2006)等。
四 从地方文化或闽学视角对朱子学进行探讨,以福建学者为代表
20世纪30年代,福建文化研究会曾探讨过福建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先河。1933和1934年,王治心先后发表了《福建理学系统》系列论文,从地域文化角度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作了系统的梳理。1935年,李兆民发表了《洛学道南系的渊源》,具体探讨了道南系理学的思想渊源。1937年,《福建文化》开辟“福建理学专号”,李兆民发表《福建理学之渊源》《紫阳理学之我见》《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等系列论文,其中《紫阳理学之我见》从宇宙观、心性说、伦理学、鬼神论四方面展开对朱熹的哲学思想作了阐述。李兆民认为周敦颐主太极说,程颐倡理气二元论,“朱子整理二家冶诸一炉,造成二元融合之一元论”,“系一元太极统系下之理气二体”。而郭毓麟在《论宋代福建理学》中则认为,“朱子学说,于哲学上,主理气二元论”。此时的研究除对朱熹及其门人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以及朱熹后学真德秀之外,还对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胡寅、胡宏等人进行研究,体现了对福建的地域文化特色。
20世纪80年代,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导下,闽学成为福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闽北闽学研究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相继成立,发掘历史文化资料,出版刊物和书籍,组织学术研讨活动,积极推动闽学研究的开展。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委党校等一批学者,采取多种合作方式,进行闽学研究,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与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和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1993)等。《福建朱子学》“将朱熹及其福建籍的弟子、再传弟子和后学汇集在一起,考察其事迹,剖析其思想”①,对福建朱子学的形成、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最有特色的研究福建朱子学的学术著作”①。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1993),探讨了闽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闽学的学术思想渊源、朱熹生平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朱熹思想体系、考亭学派、朱子学的历史命运,并附朱熹门人录(511人),大体勾勒了闽学学派这一文化群体学术流变的脉络。被认为是“对朱熹之学和考亭学派的特点及其源流,作了有特色的具体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将会促进对朱熹及其学派的更深入研究”②的一本书。此外,江西、安徽等省区的学者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朱子学进行了研究。
五 以朱子其他方面的成就为主题进行归纳整理
由于朱子本人知识广博,朱子学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对朱子某一方面成就给以归纳总结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如,关于朱子的书院、教育思想,有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李弘祺的《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等。关于朱子文学思想的有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等。归纳朱子的刻书成就的有:曹之的《朱熹与宋代刻书》、方彦寿的《朱熹刻书事迹考》(1995)、史娟的《朱熹对书院事业及图书版本馆藏的贡献——从首刻四书章句集注论及》(2007)、马刘凤、张加红的《朱熹与刻书》等。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蔡方鹿的《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等分别从美学、史学、经学等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自己的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以来港台地区对朱子学的研究
港台地区的当代朱子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当代新儒家及其弟子③,以及钱穆、劳思光①等。1958年,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阐明了当代新儒家的主要学术精神。他们上承孟子至宋明儒学的哲学思路,注重内在超越和道德实践,致力弘扬儒家道统的活的生命,追求“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并以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为儒学的“神髓”(为儒学的超越性提供了形上学保证)。同时,他们对西方文化保持一种开放性,肯定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民主和科学方化的成分,以返本开新、重建被注重道德主体的传统儒学忽略的政治主体和认识主体。尽管有这种文化担当的共识,新儒家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具体内容的理解和评价却不尽相同,关于朱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的看法亦有差异。下面就从研究方法角度对港台地区当代朱子学研究成果作一归纳。
一 会通中西方哲学,在对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宋代理学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以牟宗三为代表
与冯友兰依托西方实在论提出自己的“新理学”不同,牟宗三则在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细致梳理和解读基础上,将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进行会通。在对宋明理学判教的基础上,提出“道德的形上学”的儒学体系。在《心体与性体》中他提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心性问题,说:“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依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②由此出发,他认为朱子继承伊川理学,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还创立了儒家诠释方法,即“以客观了解为理解原则,融合根据文献和扣紧问题这一中西哲学研究特点,生命存在地呼应为进路,主客观统一为整体性、方向性原则”①。
二 采取传统学案体,借助于文化史、思想史视角,对朱子的生平、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穆、余英时等
钱穆的《朱子新学案》(1982)是继王懋竑《朱子年谱》后的史学大作,其基本立场是反对牟宗三关于朱子是“别子为宗”的观点,认为朱子“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可谓其乃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在他看来,朱子学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并不符合事实。该书有以下特点:第一,朱子对于前人的思想多有继承,并能折衷调和。朱子对伊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他对其他儒学家的思想,亦能善加摄取。第二,朱子的学问博雅深广,不仅在哲学方面建树很多,而且对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均有深入而精细的研究。第三,朱子对理学的主要概念——如,理、气、心、情、太极、阴阳,等等——均有细致而深入的剖析,并多能取一最圆融的立场。他的一个最有特色的主张,是朱子学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他的“已发未发”说、“涵养”、“省察”诸说,皆来自于他的“心”学。由此,理学与心学的区分并不像学界一贯认为的那么明显,并且,朱子的心学较陆王的心学更为圆融。后来金春峰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朱子新学案》在目录上颇像《朱子语类》,内容包罗万象,有理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学等各个方面;文献资料的选择异常广泛,几乎涉及朱子的所有相关著述,包括朱子经注以及《文集》《集注》《语类》等书。
余英时在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通过对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政治主体。余先生认为,一般哲学史论述只涉及心性、理气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缺乏对理学家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的研究分析,而此书则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在论述心性、理气之外,还有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对于现代人全面了解朱子学乃至宋明理学都具有纠偏的现实意义。
三 立足于中国哲学史,对程朱、朱陆思想进行对比,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对朱子学与西方哲学家进行比较,展现出朱子学的哲学特质
徐复观在《程朱异同——平铺地人文世界与贯通地人文世界》①中提出,朱子确实是儒家的正统道德谱系中的集大成者,但是朱子与程伊川有所不同,程子主要强调“百理俱在,平铺放着”②,并着眼于现世的一重世界,而朱子则在成德工夫上强调上下层级的贯通,并着眼于现世后面的世界、而成为二重世界。唐君毅先生热衷于会通朱陆、朱王,他的《朱陆异同探源》《朱子与陆王思想中之一现代学术意义》都表达了这种思路。唐君毅在《朱陆异同探源》③一文中表明其宗旨就在于尊朱学。唐君毅认为,“心属于气”的说法只适用于朱子的宇宙论立场,而在心性论上说,朱子并不是以气言心,而是有超乎气之动静之上的“本心”的说法,这种本心具万理、应万事,甚至不无陆王“心即理”的意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传统上认为的程朱、陆王之间的界限。在《阳明学与朱子学》中,唐君毅强调阳明的发生背景应放到朱子学背景下才有意义,才能见出前者如何比后者更进一步提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道德形上学、形上的道德学。要之,唐君毅试图证明在新儒家之中,“可以兼容并包程朱陆王等不同形态的思路,彼此不必互相冲突,而可以相反相成”④。
劳思光结合了文化思想比较,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⑤中,劳思光阐述了朱子的主要思想及其敌论(湖湘学派和事功学派),其间将朱子的思想与佛教的“空”论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对比,指出朱子思想与佛教“空”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超经验领域(即“理”领域)“须有道理”,而后者的超经验领域(即“空”领域)并无经验对象,另外,朱子的思想与亚氏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的思想更为接近(柏拉图断然区分经验世界和超经验世界,而朱子思想中的“理”与“事”并非截然二分)。不过,他对朱子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朱子治学规模虽大,但是“通过一系统性之曲解,而勾划一与历史绝不相应之‘道统’面目……实亦是构成儒学内部最大之‘混乱’也”①。
还有人将朱子与西方的托马斯·阿奎那进行比较,如1978年黎建球出版的《朱熹与多玛斯形上思想的比较》。
四 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82)兼采牟宗三的哲学分析和钱穆的考据方法。在他看来,钱穆对朱子的同情以及牟宗三所谓“别子为宗”的说法:“这两个论点分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今日研究朱子自不能不致意于钱先生的考据,牟先生的哲学思考,分析其短长,探讨其得失,则其不能够停止于二家之说,事至显然。然也不能转为调停折衷之论,必须取严格批评的态度,有一彻底融摄,然后可以对朱子产生一全新的视野。”②因此,此书既强调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来了解朱子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又结合哲学分析,只是在继承牟宗三哲学分析方法上,刘述先自言“更喜欢在康德所提供的线索之外”,开拓新的视野。尽管刘述先接受了牟宗三以朱子为“别子为宗”的看法,但他还是从客观历史出发,肯定了朱子“在内圣的修养过程以及教育程序上的贡献”,认为“足以正陆王之学的末流之失”③。
五 借助于西方诠释学理论,对朱子及其学说进行解释学剖析,展现了朱子在经典诠释上的突出成就以及朱子经典诠释的现代价值
黄俊杰在研究东亚儒家经典诠释方面成果显著,主编了《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等著述,其论文《朱子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诠释及其回响》《从朱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旧学与新知的融会》都体现出对朱子《集注》的关注。他认为,朱子的《四书集注》是以“视域融合”迈向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的动态平衡,求得“对话的”经典诠释法和“历史的”解释法之间的平衡。①张崑将从朱熹对“颜渊问仁”章的诠释出发,分析了中日儒者对朱熹的解经原则的批判,并指出后儒的解经方法仍然无法解决经典解释的歧异性。②劳悦强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出发,论述了朱熹的诠释学。③也有学者立足于中西解释学差异的角度,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存在异于西方解释学的特点。刘述先指出朱子虽擅长分析,但仍是将知识、存在、价值融贯为一体的中国哲学传统;虽强调认知,但终极目标还是圣学的实践,不是建立客观知识系统。④李清良在《朱子对理解之蔽的认识——兼论中西阐释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一文中认为朱子论理解之蔽展现了中国古典阐释理论的圆融性。梁中和在论文《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中总结出朱子解释学的三大原则:“求本意”;“实理实情”;“以身解经”,并把普通解释学与朱子解释活动进行了比较。白奚以孔子的“仁”为主轴,探讨二程与朱熹对“仁”的解释,从程朱“以体用言仁”“以生意言仁”“心之全德”等三个层次论述程朱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发展。⑤
六 运用语词分析的方式对朱子学中关键性语词给以哲学分析,凸显朱子学乃至儒学理论的特色
香港中文大学的信广来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一系列朱子学研究论文。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本考证与义理分析并重,在文本考证的基础上过渡到义理分析。应当指出的是,他所主张的义理分析并不是以达致对朱子思想的精确理解为旨归。他先是发表了一系列朱子文本考证的文章,考察朱子对一些儒家核心概念的看法,如,PurityinConfucianThought(《儒学思想中的「纯粹」观-朱熹论虚、静与私》)①,Zhu Xi on Gongand Si(《朱熹论“公”与“私”》)②,Whole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Zhu Xi onCheng,Zhong,Xin,andJing(《儒家思想中的整体观:朱熹论“诚”“忠”“信”“敬”》)③,Zhu Xi onthe“Internal”andthe“External”:A Re-sponseto ChanLee(《朱熹论“内”与“外”》)④,还有一些对朱子道德理论的整体考察的文章,如,Zhu Xi's Moral Psychology(《朱熹的道德心理学》)⑤。在此基础上,信广来又做了一些建构朱子学现代哲学体系的尝试,比如,他的On Anger-An Experimental Essay in Confucian Moral Psy-chology(《论“怒”一种儒家道德心理学的尝试》)⑥就通过比较朱子对儒家关于“怒”的思考与西方相关概念——如,indignation(愤慨)、re-sentment(忿恨)、forgiveness(宽恕)——之间的可能区别,建构出一种可以为当代人所理解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和境界论。而他的Purity,MoralTrials and Equanimity(《纯粹,道德实验与静》)⑦则是接着之前论“怒”的话题,通过比较朱子关于“诚”“虚”“静”等概念的思考与西方相关概念及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同(包括对双方理论在同一个道德实验中所可能支持的不同结果的分析),探讨一种儒家修养境界的可能性及可欲性。
七 将文献学分析与哲学理论结合起来,着重对朱熹的著述进行结构和义理的剖析
香港科技大学的陈荣开教授的朱子学研究旨在通过疏解朱子注解古代经典的方式实现两方面目标:第一,对朱子所注的古典文献有一个系统性的理解;第二,对朱子的学说有一把捉(第二个目标之所以可以通过训诂考据的方法实现,是因为朱子的学说是在他对经典的诠释中建构起来的①)。他先后发表了《朱子〈中庸〉结构说(上)》②《朱子〈中庸〉结构说(中)》③《首尾接续,血脉通贯——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章缜密结构的分析》④《朱子对〈中庸章句〉‘诚明’章的剖析与解读》⑤《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的解读》⑥等一系列文章,对朱子《中庸章句》做了细致的分章剖析和解读。陈荣开指出,虽然朱子对《中庸》的解读是以通贯经书的通篇大义为最终目标的,但朱子同时认为章句离析是义理解读的必要条件,而他则秉承朱子的宗旨,从章句离析入手,对朱子的《中庸章句》进行解读。他的一系列文章均旨在剖析《中庸章句》的复杂结构,并借此重建《中庸》学的整体架构。陈荣开认为,《中庸章句》虽不像《大学章句》那样对经书做出了“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的大胆编排,却将经文彻底地重分为三十三章、一百三十节,比对于既有郑注孔疏版本,分章断节的改动不可谓不大。而对于《中庸章句》本身的分段,陈荣开未采用以往的“四大支”“三大段”“四大段落”等分法,而是采用了五段式分法:首章和尾章各自成一段,第二至第十一章(共十章)为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章(共九章)为第三段,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共十章)为第四段。在《朱子〈中庸〉结构说(上)》中,陈荣开分析了第一、第二段。对于第一段,陈荣开以图表一帧,指示结构,纵分纲领、中、和,横分性与道、教、效,并按类相从地详细引述了《中庸》经文和朱子所加的注,既而指出第一大段纲举目张地指示了性、道、教三个基本范畴的内在联系,中、和的分别是道的体、用,致中、致和分别是涵养、省察的要诀和达致天地位、万物育的基本功夫。对于第二段,陈荣开也以图表一一显示其内在结构,继而按章节分析其内在关联:第二章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原因,第三章指出中庸之为至德久为民所鲜能的事实,第四章根据这一事实剖析道不行和道不明的原因,第五章和第七章分别带出道不明与不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第六章和第八章分别以舜和颜渊为例,说明道之得行、得明的依凭所在,亦即知、仁这两个造道成德之法。第九章以子路之勇为例,指出知、仁若不纯熟,则不可能达到中庸,呼应了第三章中中庸民所鲜能的事实,第十、第十一章以强勇为主题,分别侧重于勇的程度适中的必要性及勇之所发的恰当性。
在专注于朱子学的学术研究之外,又有对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综述,如,台湾的林庆彰著有《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1992),吴展良著有《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2007),展现了21世纪国内外朱子学研究的丰厚成果。
依照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内朱子学研究可以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为界,大致划分为两阶段: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20世纪后中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总结20世纪前的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可以归纳为儒学内部对朱子学的修正。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子距今仅八百年,后人之阐发容未能尽。而反朱攻朱者,多不出于百家众流,而转多出于儒学之同门。”“诤朱攻朱,其说亦全从朱子学说中来。”①综观20世纪以后国内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则鲜有纯粹从儒学内部阐发朱子学的现象,而是普遍从西方哲学、史学等现代学科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朱子学涵盖甚广,既包括了朱熹本人及其弟子后学的思想学说,也包括了深受朱子学影响的“东亚文化圈”之中的思想家对朱子学说的阐释,这就意味着朱子学研究综述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绝非本章所能囊括。因此,本章的“朱子学”仅限于后人对朱子本人学说的阐发和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
20世纪以前,因为统治者推崇的缘故,一方面朱子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既控制着庙堂之上的思想倾向,也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当中;另一方面朱子学作为涉及理气、心性等本体功夫论的学说体系,深深吸引着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朱子学说做出自己的解读。于是“述朱阐朱”成为“中国学术上一大争议”②,这些“学术争议”大体可依对待朱子学的态度分为两方面:一是朱门后学以及官方对朱子学的继承和阐发;二是陆王心学、气本论、事功学派、汉学等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发展。具体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 朱门后学对朱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与陆王心学相比,朱门弟子众多,再加上朱学普遍重视读经注经、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因此朱学在朱子去世后一直连绵不绝,即便是在明中期阳明学兴起之后、清代汉学盛行之时,朱子学派也从未中断。但是由于朱子对理学的义理阐发可以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朱门后学对朱子理学的新发展微乎其微,基本停留在对理气、心性、格致等传统理学的阐释上;与朱子理学相较,朱子对《四书》学、《五经》学的注释、解读却为后学留下了一定发展空间。于是朱子弟子及其后学主要是在对朱子四书学、五经学、小学等著述的阐释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在朱子的亲炙弟子中,陈淳著有《四书性理字义》和《严陵讲义》。前者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二十五个范畴,是后世理解《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后者则全面继承朱子理学思想,是后世理解朱子理学范畴的重要参考书。黄榦继承了朱子《礼》学思想,与杨复一起续补修成朱子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同时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继承了朱子对《五经》《四书》的基本观点。蔡元定和蔡沈父子对朱子的象数易作了进一步发展,蔡元定著有《皇极经世指要》,概括了邵雍的思想,蔡沈著有《洪范皇极》,发展了理学象数学。同时,蔡沈还依照朱子的嘱托,以“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为宗旨,完成《书集传》,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尚书》思想。朱子向来看重小学,亲自编纂蒙学读物,在其弟子当中,程端蒙著有《性理字训》,朱子认为:“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①程端蒙还同董铢合作制定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对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作了总体规划。由于朱门弟子一向有重视读书著述的传统,所以朱门弟子对《四书》、《五经》、小学、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而像《北溪字义》《书集传》《性理字训》等朱学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南宋朱子后学一方面为朱子学的传播及其上升为官学做出努力,以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另一方面则继续阐发朱子理学、经学等思想,为朱子学传承至元明奠定基础,以黄震、“金华四先生”为代表。真德秀早年从游于朱子弟子詹体仁,他所著《大学衍义》是对朱子《大学章句》的阐释,深得当时乃至后世皇帝的重视。魏了翁著有《九经要义》,主要是注疏释文,对朱子的理学思想鲜有发展。真德秀、魏了翁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推动了朱子学由“伪学”最终转变为官学。黄震是朱子弟子辅广的三传弟子,他的《黄氏日抄》是读经史子集的札记,其中不乏有对程朱思想的批评和修正。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均属黄榦后学。何基从学于黄榦,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莫不以朱学为依归。王柏从学于何基,金履祥从学于王柏,许谦从学于金履祥,他们在五经、四书、理学等方面都有大量著述流传后世。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柏、金履祥继承了朱子“疑经”的传统,王柏著有《诗疑》《书疑》《大学沿革后论》《中庸论》,金履祥著有《尚书注》《论孟集注考证》等,对传统四书五经,乃至朱子著作和学说都提出很多疑问。金华朱学直接影响到元代乃至明初理学。
元代许衡、刘因、吴澄等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许衡在元朝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这与其不遗余力地传播朱子学、积极推动《四书集注》在延祐年间定为科场程式有关。许衡虽继承朱学,但并没有严守朱学门户,其心性论游离于朱子“穷理以明心”和陆象山“明心以穷理”之间。刘因极力推崇朱子,认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①。他对理学和经学、史学的关系上看法独到,认为理学本于六经,“古无经史之分”,即《诗》《书》《春秋》等经就是史,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对经学、理学、史学的看法。吴澄拜饶鲁弟子程若庸为师,饶鲁则是黄榦的高弟。吴澄以接续朱子为己任,著有《五经纂言》,发展了朱子学。其中,吴澄在三礼上的成就深受后人肯定。在三礼上,吴澄依朱子的端绪和规模,“以《仪礼》为纲”,“重加伦纪”,全祖望谓“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由之,用功最勤”②。许衡与吴澄都以朱学为标帜,但他们由朱学的心外格物,移到陆学的直求本心,是宋代程朱理学发展为明代王学的过渡。
明朝中后期几乎是阳明心学的天下,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明朝初期,代表人物有宋濂、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宋濂传承了金华朱学,因其喜援佛入儒,认为儒佛“本一”,所以全祖望称之为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宋濂认为,吾心为“天下最大”,识心明心是“不假外求”的内向冥悟,体现出元末明初理学调和朱陆的倾向。曹端被清人认为“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③。曹端发展了朱子理气论,他反对朱子把太极与动静、理与气看成二物,认为太极自能动静,因此不同意朱子所谓理气如人之乘马的比喻。薛瑄发挥朱子“理气相即”的观点,抛弃了所谓“理先气后”的提法,在曹端提出的“理气未尝有间隙”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理气关系。与薛瑄偏于下学相比,吴与弼则侧重于“寻向上工夫”。吴与弼主张静观修养论。其弟子分为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①,这一派观点与王阳明心学相似;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②,这一派仍有朱子学之风。待到阳明心学昌行,朱子学作为官学,已是徒具形式,思想上毫无创见。当王学末流弊端逐渐显露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重新推崇朱学,遵奉“性即理”“居敬穷理”“格物穷理”,以朱学批判佛学和王学,但对朱子学体系并无明显发展。
明末清初朱子学仍有信奉者,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为代表,对朱子学说以维护信奉为主,在学说创见上并无太大功绩。陆世仪否认理游离于事物之外,反对离气质而言性,强调“人性之善正在于气质”。他还发展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说。陆陇其极力尊崇朱子学,贬抑阳明学。他继承了朱子“理之流行”说和“居敬穷理”论。李光地著作宏丰,遍及四书、五经。他虽学宗程朱,但并未全盘肯定朱子学。其理学的最高范畴是“性”,而不是“理”或“心”,主张“性为本气为具”的性气观。李光地奉命编纂《性理精义》等大量理学著作,对朱子学著作的整理和传播颇有贡献。
二 官方对朱子学的阐释和利用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庆元至嘉定的二十余年间,一直受到禁锢。后来在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极力提倡下,宋理宗逐渐确立理学为国是。元仁宗延祐年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标准,《四书》主朱子的《四书集注》,《易》主《程氏易传》,《书》主蔡沈《书集传》,《诗》主朱子《诗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于是,朱子学在元朝通过科考正式成为官学。
明清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经传、集注以及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出版,其目的并不在于发明理学义理,而在于以钦定形式确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使之更好为科举考试服务,进而为他们的统治服务。明永乐十三年,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作为教授生徒、科举考试的准绳。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周易大全》依据《伊川易传》及朱子《易本义》,《书传大全》依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子《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主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乃朱子弟子,陈澔之父大猷师饶鲁,饶鲁师黄榦。所以《五经大全》所据传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四书大全》是对《四书集注》的进一步扩充,其中所引用“先儒”之说,有106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程朱学派中人,以朱子弟子及后学为主。《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也十分明显,卷首所列“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程朱学派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所收先儒著作,或为朱子所注,或为朱子所作,或为朱子门人所作。其中语录的编排体例完全模仿《朱子语类》的门目。
清朝初年,在康熙帝推动下,李光地等人奉命编纂了《性理精义》。《性理精义》是《性理大全》的精简本,主要选取宋元时期四十五位理学家论学、论性命、论理气、论治道等若干言论而成,其主要思想、观点、材料都在《性理大全》的范围内。除《性理精义》之外,李光地奉命编订的性理之书还有:编《朱子语类四纂》五卷(康熙三十四年);《二程遗书纂》二卷(康熙三十五年);《朱子礼纂》五卷(康熙四十六年);奉命与熊赐履等编《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等。《朱子全书》是从《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类编次”而成。在李光地编纂的系列著述中,《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费力最大、影响最大,可以说,这二书代表了清朝官方对朱子学的基本理解,因为不仅它们的编纂工作是在康熙直接主持下进行的,而且康熙亲自审订其宗旨、体例、选材、编次以至校刊,并为之作序。直到1905年,《大全》《精义》等官学著述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才彻底告别了过去一统天下的时代。朱子学也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新文化运动而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殿堂,在近现代学术界常常被看作中国学术思想史当中的一个学派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三 陆王心学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吸收
陆王学派与朱学同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所以陆王学派对朱学的批判或融合仍属于传统理学内部的讨论。由于陆九渊不像朱子那样重视著书立说,所以陆九渊去世后,其弟子对陆学的认识已经很模糊,以至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朱学思想。陆九渊的弟子包扬,“及象山卒,即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槐堂诸儒学案》)包扬之子包恢,史称“少得朱陆渊源之学”。包恢弟子龚霆松则有“朱陆忠臣”之称,著有《四书朱陆会同注释》。南宋陆学的主要人物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是同乡,被称为“甬上四学者”,其中舒璘、沈焕也都表现出折中朱陆的倾向。舒璘曾与朱子书信往来,一度对朱子的致学方法及其推崇的“二图”(先天图,太极图)提出质疑。沈焕对朱子一直表示尊敬,丝毫没有朱陆对立的痕迹。
明代陈献章和湛若水继承并发展了吴与弼的思想,他们都不否认朱学,对朱陆基本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王阳明心学则是源于对朱子理学的改造。王阳明曾经“泛滥辞章”“遍读考亭遗书”,致力朱子学,年轻时曾亲身实践朱子的格物穷理说,一连七天静坐试图“格”竹子之理,最终失败。后来王阳明逐渐放弃了朱子学,提出了与朱子的天理论、格物说、知行说等对立的心学体系。王阳明反对朱子的“性即理”,主张“心外无理”;反对朱子的“知先行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朱子对“格物”的解释,提出以《尚书》中的“格其非心”为例,“格物”的“格”,不能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但阳明心学依然沿用朱子学的很多理学范畴,比如他最著名的“致良知”说仍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容的。
明末清初,王学末流弊端显现,于是心学内部出现了借鉴朱子理学修正心学的倾向。刘宗周提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把朱子的“无一毫人欲之私”的“第一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联系起来,希望能够实现“克去人欲之私”的目的。黄宗羲也试图通过“道问学”以成就“尊德性”,一改不重读书著述的心学传统,提倡读书,注重研究经史和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这明显带有朱学的特点。不过黄宗羲的基本立场仍是心学,所以在其《宋元学案》中评价朱陆时明显表现出右陆左朱。
无论官学的支持利用还是心学的批判无不是从遵奉宋明理学这个大前提出发的,而以下三种对朱子学的批判则着眼于批判整个宋明理学——包括朱学、陆学、王学。这是因为,到了明末清初,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经历了长期发展之后,迟迟没有产生新理论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程朱陆王展开批判,以期创立一种能够改变甚至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宋明理学。
四 从气本论角度出发批判和发展朱子学
在明朝中后期王学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从气本论角度批判朱子理学的理学家,以罗钦顺、王廷相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以张载的气本论为依据,对朱子的理气论进行了检讨,提出了自己的理气说。黄宗羲评价罗钦顺:“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又说:“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罗钦顺认为气是最根本者,理只是气之条理,理在气中而非与气对立,这与朱子理先气后思想明显不同。王廷相在其《慎言》中表达了“气本”论。他认为并非气本于理,而是理根于气。他批评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说,提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的命题。他还将“性理”气化,批评程朱理学的“性即理”,否认存在先天的“德性之知”,由此也就否认了性善论。在修养论上,他既反对程朱的“体认天理”,又反对陆王的“讲求良知”,独以张载为宗。
在明末清初,王夫之继承张载的气本论,反对朱子将理与气二分,认为气是宇宙中根本,无气则无理。“理在气中,气无非理。”他认为理即秩序,且即气之秩序。在形上形下关系上,他认为形而下之“器”是根本,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所谓“天下惟器而已,道者器之道”。他认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他批判朱子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结论。
五 从实学出发对朱子学的批判
颜元、李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不仅对朱、陆、王进行批判,而且直接批评周、程、张、邵等理学开创者,认为理学家声言“明体达用”,其实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他们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其实源于佛老。颜李学派以陈亮的事功学作为出发点,他们常常讨论的话题有:理事、体用、动静、知行、形性、性习、道艺、义利等。他们反对“理在事上”“理气二本”,主张“理在事中”“理气一致”。他们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敬持敬的心性修养,注重实践,崇尚技艺,讲求功用。他们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肯定人欲的合理性。颜元著有《四存编》《朱子语类评》《四书正误》《习斋记余》等,内容均以批判朱子为主。严格说来,颜李学派与理学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在根本上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颜李学派反对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致用”的实学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之下理学日渐衰退的必然反动。
六 从汉学角度出发对朱子学的批判与发展
清代学术以汉学最为辉煌,是作为宋学的对立面出现的,顾炎武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顾炎武试图以经学家的见地来改造理学,朱子在他心中的形象,与其说是理学家,倒不如说是重视训诂、明于典章制度的经学家。顾炎武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对经学考辨精审。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的观点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转向。清代朴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疑经的传统,传统儒家经典无不遭到质疑、考辨。如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古文尚书》及其《孔安国传》为伪书,这发展了朱子疑《古文尚书》的观点。毛奇龄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专辨象数图书;胡渭的《易图明辨》,专辨《河图》《洛书》。由于“无极”“太极”《河图》《洛书》是“宋学”的根本,宋代理学家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所以毛奇龄、胡渭对图书的考辨无疑触及了宋代理学的基石。姚际恒著有《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毛奇龄著有《四书改错》,专门针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认为朱子注几于无一条不错。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这些著述无不继续发扬着朱子的疑经作风,只是他们大都以批判朱子的经学传注为目标。
汉学家在全力批判朱子经注时,并不意味着贬抑朱子。阎若璩曾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惠士奇尝手书楹联曰:“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可见他们虽尊汉但并不反宋。江永也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作《近思录集注》,对朱子著作进行阐释。陈澧著有《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并不排斥注疏,相反提倡读注。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批驳汉学,尊崇宋学。清儒除批判朱子著述外,又有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对朱子的生平进行考证,是以汉学路子研究朱子的典范。
总起来说,从朱门后学对朱子学的阐发至颜李学派对朱子学的批判,无不从朱子学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说、经学传注等方面入手的,他们述朱攻朱的出发点无不从“经世致用”的儒学角度出发,直到清代早期顾炎武、阎若璩等虽以考证方法治经但仍在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与理学家由格致诚正以求修齐治平的为学目标是一贯的。这种治学的目标和方式与近现代“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并不一致。随着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汉学家渐渐放弃了“致用”的幻想,而走向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治学路径。因而,梁启超先生说:“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①又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②这种“科学精神”已经接近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了。
第二节 20世纪后中国大陆对朱子学的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渐渐被西方学科分类所取代,于是,朱子学研究出现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划分,其中以哲学研究朱子学的成就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前朱子学研究方法多样,视野广阔,成就斐然,特别突出的是一些哲学家运用西方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和发展朱子学,进而提出新的哲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去看待和评介朱子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对朱子学基本持批判、否定态度,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乏善可陈。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环境日趋宽容开放,学者对朱子学的各种研究也逐渐能够秉持客观公允的基本立场,不仅对朱子学的哲学研究成果突出,而且从史学、文献学角度对朱子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辉煌的学术成果。以下将从哲学、史学、文献学及其他四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国内朱子学研究方法做一归纳。
一 哲学角度
大陆从哲学上研究朱子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冯友兰,他通过对朱子理学的深入剖析,创立新理学体系,从理论体系上发展了朱子学。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则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朱子学的某一方面进行归纳分析,向现代读者展示出异彩纷呈的朱子学。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估朱子学;以陈来为代表的学者专注于分析朱子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张立文为代表的学者着重于比较朱子学与其他学者或学派的异同;以蔡方鹿、朱汉民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西方解释学角度出发分析朱子学。
(一)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结合相关文献,深入剖析朱子理学,从而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冯友兰为代表。
冯友兰在抗战时期著成《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了新理学体系。所谓新理学就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所谓“接着”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的理学。一方面,冯友兰把朱子学的精髓转换为“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内在要素;另一方面,他又以哲学家的视域反观朱子学。冯友兰运用“以西释中”的框架对朱子学进行了诠释,他说:“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著力。”①冯友兰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朱子学当中的理、气、心、性等概念进行分析。在《新理学》中,他依照“新实在论”把理世界解释的真际世界,气世界解释为实际世界,认为理世界与气世界构成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朱子学进行重新评价,主要体现在建国后大陆编纂的《中国哲学史》之中,以任继愈、侯外庐、邱汉生、冯友兰等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自古存在唯物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从唯物、唯心角度评价朱子哲学的。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年版)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63年版)中,朱子都是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被批判的。侯外庐、邱汉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1987年版)也受到哲学史研究的影响,由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发展出“理学与反理学”的模式,继续表彰反理学的思想家,朱子学仍是作为唯心主义者受到批判。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1980年版)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四书集注》做了论述。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诠释框架,对朱子学做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道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朱子学既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也是后期道学的肯定阶段。他还说:“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②
另外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1981年版)、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影响。
(三)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年版),基本兼采哲学范畴的分析与文献资料的考证的方法,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朱陆异同等问题的产生、演变做了深入的考辨和分析。陈荣捷认为此书“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特别提到陈来对理气先后的考证足以“补冯友兰等学者逻辑推究说之不足”①。
近年来有学者引入发生学的概念,对朱子学进行分析。2010年丁为祥发表《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在他看来,牟宗三、刘述先对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指其“哲学理论逻辑(所谓内在必然性、架构性)或思想谱系性的展开,与朱子本人的人生现实并不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于是他主张从朱子的生存心态、学术性格等主体性因素出发,对朱子思想进行发生学的解释,试图解答朱子的哲学视野、思想体系、历史影响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等问题。2012年丁为祥出版《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阐发。
(四)比较方法研究朱子学。
张立文的《朱熹与退溪思想之比较研究》(1995年版)将朱子与朝鲜的李退溪进行比较。又有不少学者常常将朱子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如冯友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等范畴来解释朱子的理气说,他认为朱子所谓“月印万川”与柏拉图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都是为了解释一与多的关系,朱子的修养方法,也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2011年刘光顺以《宇宙生成论的中西比较——以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例》为题对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比较。潘德荣则将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进行比较,他在《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中指出,朱子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视为经典解释的第一目标,施莱尔马赫则把揭示作者的原意视为解释的根本目的。
(五)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研究朱子理学和注经的关系,一方面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注经与创立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出中西解释学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从2000年出现延续至今,以蔡方鹿、朱汉民等为代表。
有的学者对朱子学的解释学进行归纳概括,如蔡方鹿分析了朱子经学、理学、哲学的关系,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学融合了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形成较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潘德荣在论文《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提出“理”是朱子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朱汉民则在论文《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中,指出朱子是运用“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刘笑敢以《论语集注》为例,提出“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概念,强调在一般的经典诠释中,有“两种定向”“两个标准”。朱熹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形式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何俊以《论语·学而》篇首章的四种诠释为例,论证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他认为朱熹以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归宿,融合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使宋代儒学在方法和思想两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①
二 采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借助于传记体等传统形式,对朱子的生平、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束景南、张立文、高令印等
束景南的《朱子大传》(1992)“是一部心态研究之书,是用传记体的形式研究道学文化心态的著作”②。作者采用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探讨朱子的一生与思想发展历程,所谓“文化还原”法是相对于那种“把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理‘过滤’为一般的哲学原理、人生信条与政治原则”的“古典”研究方法而言,它“是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念与政治追求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具体——可以称为活的文化还原法”③。另外,学界还有两部《朱熹评传》,全面阐述了朱子的生平与思想,一部是陈正夫、何植靖合著,一部是张立文所著。除梳理朱子的思想变化外,还有对朱子的活动、事迹的考证、分析。比如,高令印在1987年版的《朱熹事迹考》,是结合实地调查对朱子的主要事迹做考证。束景南在2001年出版的《朱熹年谱长编》对朱子一生中的重大的学术活动作了详细记述、按评。
三 从文献学角度,对朱子的著作及其文献学贡献进行考证与梳理,以陈来、束景南、白寿彝等为代表
由于朱子的著述宏丰,完成时间不详,所以有很多学者对朱子的相关著述的年代进行考证。1989年陈来出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是对朱子书信的年期作考订,陈荣捷评价此书道:“数量之多,考据之实,远出乎王懋竑《朱子年谱》与钱穆《朱子新学案》之上。”①陈来又有《朱熹观书诗小考》《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等论文对朱子相关著述做了考证。束景南在1991年出版的《朱熹佚文辑考》对朱子诗文、书信、著作、语录等的年限进行了考证。对朱子著作进行考证的论文还有:钦伟刚在2004年发表的《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考》、杨文森于2007年发表的《朱熹证伪古文尚书及序、传详考》、李永明于2008年发表《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赵振于2007年发表的《朱熹与二程语录的整理与编辑》。除此之外,华东师大出版社对朱子著作进行整理出版,为现代朱子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在2010年,为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朱子著述宋刻集成》《朱子全书外编》《朱子全书》(修订版)三套图书。
除对朱子著述进行研究、整理之外,又有学者对朱子的文献学成就进行归纳总结。白寿彝在1933年出版的《朱熹辨伪书语》所辨书近五十种,体例是将《语类》和《文集》中关于朱子辨伪的资料列于所要考辨书籍之下。1987年,王余光和钱婉约发表《朱熹在辨伪学上的成就和影响》,1988年,孙钦善发表《朱熹与古文献学》都对朱子的文献学成就进行了梳理。相关主题的论文还有叶建华的《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1990),曾贻芬的《朱熹的注释和辨伪》(1993),华星白的《朱熹的古籍注释》,杨绪敏的《朱熹考辨古书真伪的成就、方法及影响》(2006)等。
四 从地方文化或闽学视角对朱子学进行探讨,以福建学者为代表
20世纪30年代,福建文化研究会曾探讨过福建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先河。1933和1934年,王治心先后发表了《福建理学系统》系列论文,从地域文化角度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作了系统的梳理。1935年,李兆民发表了《洛学道南系的渊源》,具体探讨了道南系理学的思想渊源。1937年,《福建文化》开辟“福建理学专号”,李兆民发表《福建理学之渊源》《紫阳理学之我见》《明清福建理学诸家之概况》等系列论文,其中《紫阳理学之我见》从宇宙观、心性说、伦理学、鬼神论四方面展开对朱熹的哲学思想作了阐述。李兆民认为周敦颐主太极说,程颐倡理气二元论,“朱子整理二家冶诸一炉,造成二元融合之一元论”,“系一元太极统系下之理气二体”。而郭毓麟在《论宋代福建理学》中则认为,“朱子学说,于哲学上,主理气二元论”。此时的研究除对朱熹及其门人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以及朱熹后学真德秀之外,还对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胡寅、胡宏等人进行研究,体现了对福建的地域文化特色。
20世纪80年代,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导下,闽学成为福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闽北闽学研究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相继成立,发掘历史文化资料,出版刊物和书籍,组织学术研讨活动,积极推动闽学研究的开展。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委党校等一批学者,采取多种合作方式,进行闽学研究,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与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和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1993)等。《福建朱子学》“将朱熹及其福建籍的弟子、再传弟子和后学汇集在一起,考察其事迹,剖析其思想”①,对福建朱子学的形成、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最有特色的研究福建朱子学的学术著作”①。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1993),探讨了闽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闽学的学术思想渊源、朱熹生平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朱熹思想体系、考亭学派、朱子学的历史命运,并附朱熹门人录(511人),大体勾勒了闽学学派这一文化群体学术流变的脉络。被认为是“对朱熹之学和考亭学派的特点及其源流,作了有特色的具体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将会促进对朱熹及其学派的更深入研究”②的一本书。此外,江西、安徽等省区的学者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朱子学进行了研究。
五 以朱子其他方面的成就为主题进行归纳整理
由于朱子本人知识广博,朱子学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对朱子某一方面成就给以归纳总结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如,关于朱子的书院、教育思想,有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李弘祺的《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等。关于朱子文学思想的有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等。归纳朱子的刻书成就的有:曹之的《朱熹与宋代刻书》、方彦寿的《朱熹刻书事迹考》(1995)、史娟的《朱熹对书院事业及图书版本馆藏的贡献——从首刻四书章句集注论及》(2007)、马刘凤、张加红的《朱熹与刻书》等。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蔡方鹿的《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等分别从美学、史学、经学等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自己的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以来港台地区对朱子学的研究
港台地区的当代朱子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当代新儒家及其弟子③,以及钱穆、劳思光①等。1958年,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阐明了当代新儒家的主要学术精神。他们上承孟子至宋明儒学的哲学思路,注重内在超越和道德实践,致力弘扬儒家道统的活的生命,追求“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并以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为儒学的“神髓”(为儒学的超越性提供了形上学保证)。同时,他们对西方文化保持一种开放性,肯定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民主和科学方化的成分,以返本开新、重建被注重道德主体的传统儒学忽略的政治主体和认识主体。尽管有这种文化担当的共识,新儒家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具体内容的理解和评价却不尽相同,关于朱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的看法亦有差异。下面就从研究方法角度对港台地区当代朱子学研究成果作一归纳。
一 会通中西方哲学,在对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宋代理学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以牟宗三为代表
与冯友兰依托西方实在论提出自己的“新理学”不同,牟宗三则在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细致梳理和解读基础上,将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进行会通。在对宋明理学判教的基础上,提出“道德的形上学”的儒学体系。在《心体与性体》中他提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心性问题,说:“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依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②由此出发,他认为朱子继承伊川理学,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还创立了儒家诠释方法,即“以客观了解为理解原则,融合根据文献和扣紧问题这一中西哲学研究特点,生命存在地呼应为进路,主客观统一为整体性、方向性原则”①。
二 采取传统学案体,借助于文化史、思想史视角,对朱子的生平、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穆、余英时等
钱穆的《朱子新学案》(1982)是继王懋竑《朱子年谱》后的史学大作,其基本立场是反对牟宗三关于朱子是“别子为宗”的观点,认为朱子“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可谓其乃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在他看来,朱子学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并不符合事实。该书有以下特点:第一,朱子对于前人的思想多有继承,并能折衷调和。朱子对伊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他对其他儒学家的思想,亦能善加摄取。第二,朱子的学问博雅深广,不仅在哲学方面建树很多,而且对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均有深入而精细的研究。第三,朱子对理学的主要概念——如,理、气、心、情、太极、阴阳,等等——均有细致而深入的剖析,并多能取一最圆融的立场。他的一个最有特色的主张,是朱子学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他的“已发未发”说、“涵养”、“省察”诸说,皆来自于他的“心”学。由此,理学与心学的区分并不像学界一贯认为的那么明显,并且,朱子的心学较陆王的心学更为圆融。后来金春峰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朱子新学案》在目录上颇像《朱子语类》,内容包罗万象,有理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学等各个方面;文献资料的选择异常广泛,几乎涉及朱子的所有相关著述,包括朱子经注以及《文集》《集注》《语类》等书。
余英时在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通过对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政治主体。余先生认为,一般哲学史论述只涉及心性、理气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缺乏对理学家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的研究分析,而此书则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在论述心性、理气之外,还有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对于现代人全面了解朱子学乃至宋明理学都具有纠偏的现实意义。
三 立足于中国哲学史,对程朱、朱陆思想进行对比,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对朱子学与西方哲学家进行比较,展现出朱子学的哲学特质
徐复观在《程朱异同——平铺地人文世界与贯通地人文世界》①中提出,朱子确实是儒家的正统道德谱系中的集大成者,但是朱子与程伊川有所不同,程子主要强调“百理俱在,平铺放着”②,并着眼于现世的一重世界,而朱子则在成德工夫上强调上下层级的贯通,并着眼于现世后面的世界、而成为二重世界。唐君毅先生热衷于会通朱陆、朱王,他的《朱陆异同探源》《朱子与陆王思想中之一现代学术意义》都表达了这种思路。唐君毅在《朱陆异同探源》③一文中表明其宗旨就在于尊朱学。唐君毅认为,“心属于气”的说法只适用于朱子的宇宙论立场,而在心性论上说,朱子并不是以气言心,而是有超乎气之动静之上的“本心”的说法,这种本心具万理、应万事,甚至不无陆王“心即理”的意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传统上认为的程朱、陆王之间的界限。在《阳明学与朱子学》中,唐君毅强调阳明的发生背景应放到朱子学背景下才有意义,才能见出前者如何比后者更进一步提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道德形上学、形上的道德学。要之,唐君毅试图证明在新儒家之中,“可以兼容并包程朱陆王等不同形态的思路,彼此不必互相冲突,而可以相反相成”④。
劳思光结合了文化思想比较,援引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和思想分析朱子思想。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⑤中,劳思光阐述了朱子的主要思想及其敌论(湖湘学派和事功学派),其间将朱子的思想与佛教的“空”论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对比,指出朱子思想与佛教“空”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超经验领域(即“理”领域)“须有道理”,而后者的超经验领域(即“空”领域)并无经验对象,另外,朱子的思想与亚氏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的思想更为接近(柏拉图断然区分经验世界和超经验世界,而朱子思想中的“理”与“事”并非截然二分)。不过,他对朱子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朱子治学规模虽大,但是“通过一系统性之曲解,而勾划一与历史绝不相应之‘道统’面目……实亦是构成儒学内部最大之‘混乱’也”①。
还有人将朱子与西方的托马斯·阿奎那进行比较,如1978年黎建球出版的《朱熹与多玛斯形上思想的比较》。
四 从朱子学的历史演变入手,综合文献考证与哲学分析的方法,力图全面阐述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82)兼采牟宗三的哲学分析和钱穆的考据方法。在他看来,钱穆对朱子的同情以及牟宗三所谓“别子为宗”的说法:“这两个论点分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今日研究朱子自不能不致意于钱先生的考据,牟先生的哲学思考,分析其短长,探讨其得失,则其不能够停止于二家之说,事至显然。然也不能转为调停折衷之论,必须取严格批评的态度,有一彻底融摄,然后可以对朱子产生一全新的视野。”②因此,此书既强调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来了解朱子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又结合哲学分析,只是在继承牟宗三哲学分析方法上,刘述先自言“更喜欢在康德所提供的线索之外”,开拓新的视野。尽管刘述先接受了牟宗三以朱子为“别子为宗”的看法,但他还是从客观历史出发,肯定了朱子“在内圣的修养过程以及教育程序上的贡献”,认为“足以正陆王之学的末流之失”③。
五 借助于西方诠释学理论,对朱子及其学说进行解释学剖析,展现了朱子在经典诠释上的突出成就以及朱子经典诠释的现代价值
黄俊杰在研究东亚儒家经典诠释方面成果显著,主编了《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等著述,其论文《朱子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诠释及其回响》《从朱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旧学与新知的融会》都体现出对朱子《集注》的关注。他认为,朱子的《四书集注》是以“视域融合”迈向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的动态平衡,求得“对话的”经典诠释法和“历史的”解释法之间的平衡。①张崑将从朱熹对“颜渊问仁”章的诠释出发,分析了中日儒者对朱熹的解经原则的批判,并指出后儒的解经方法仍然无法解决经典解释的歧异性。②劳悦强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出发,论述了朱熹的诠释学。③也有学者立足于中西解释学差异的角度,认为朱子经典诠释存在异于西方解释学的特点。刘述先指出朱子虽擅长分析,但仍是将知识、存在、价值融贯为一体的中国哲学传统;虽强调认知,但终极目标还是圣学的实践,不是建立客观知识系统。④李清良在《朱子对理解之蔽的认识——兼论中西阐释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一文中认为朱子论理解之蔽展现了中国古典阐释理论的圆融性。梁中和在论文《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中总结出朱子解释学的三大原则:“求本意”;“实理实情”;“以身解经”,并把普通解释学与朱子解释活动进行了比较。白奚以孔子的“仁”为主轴,探讨二程与朱熹对“仁”的解释,从程朱“以体用言仁”“以生意言仁”“心之全德”等三个层次论述程朱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发展。⑤
六 运用语词分析的方式对朱子学中关键性语词给以哲学分析,凸显朱子学乃至儒学理论的特色
香港中文大学的信广来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一系列朱子学研究论文。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本考证与义理分析并重,在文本考证的基础上过渡到义理分析。应当指出的是,他所主张的义理分析并不是以达致对朱子思想的精确理解为旨归。他先是发表了一系列朱子文本考证的文章,考察朱子对一些儒家核心概念的看法,如,PurityinConfucianThought(《儒学思想中的「纯粹」观-朱熹论虚、静与私》)①,Zhu Xi on Gongand Si(《朱熹论“公”与“私”》)②,Whole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Zhu Xi onCheng,Zhong,Xin,andJing(《儒家思想中的整体观:朱熹论“诚”“忠”“信”“敬”》)③,Zhu Xi onthe“Internal”andthe“External”:A Re-sponseto ChanLee(《朱熹论“内”与“外”》)④,还有一些对朱子道德理论的整体考察的文章,如,Zhu Xi's Moral Psychology(《朱熹的道德心理学》)⑤。在此基础上,信广来又做了一些建构朱子学现代哲学体系的尝试,比如,他的On Anger-An Experimental Essay in Confucian Moral Psy-chology(《论“怒”一种儒家道德心理学的尝试》)⑥就通过比较朱子对儒家关于“怒”的思考与西方相关概念——如,indignation(愤慨)、re-sentment(忿恨)、forgiveness(宽恕)——之间的可能区别,建构出一种可以为当代人所理解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和境界论。而他的Purity,MoralTrials and Equanimity(《纯粹,道德实验与静》)⑦则是接着之前论“怒”的话题,通过比较朱子关于“诚”“虚”“静”等概念的思考与西方相关概念及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同(包括对双方理论在同一个道德实验中所可能支持的不同结果的分析),探讨一种儒家修养境界的可能性及可欲性。
七 将文献学分析与哲学理论结合起来,着重对朱熹的著述进行结构和义理的剖析
香港科技大学的陈荣开教授的朱子学研究旨在通过疏解朱子注解古代经典的方式实现两方面目标:第一,对朱子所注的古典文献有一个系统性的理解;第二,对朱子的学说有一把捉(第二个目标之所以可以通过训诂考据的方法实现,是因为朱子的学说是在他对经典的诠释中建构起来的①)。他先后发表了《朱子〈中庸〉结构说(上)》②《朱子〈中庸〉结构说(中)》③《首尾接续,血脉通贯——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章缜密结构的分析》④《朱子对〈中庸章句〉‘诚明’章的剖析与解读》⑤《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的解读》⑥等一系列文章,对朱子《中庸章句》做了细致的分章剖析和解读。陈荣开指出,虽然朱子对《中庸》的解读是以通贯经书的通篇大义为最终目标的,但朱子同时认为章句离析是义理解读的必要条件,而他则秉承朱子的宗旨,从章句离析入手,对朱子的《中庸章句》进行解读。他的一系列文章均旨在剖析《中庸章句》的复杂结构,并借此重建《中庸》学的整体架构。陈荣开认为,《中庸章句》虽不像《大学章句》那样对经书做出了“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的大胆编排,却将经文彻底地重分为三十三章、一百三十节,比对于既有郑注孔疏版本,分章断节的改动不可谓不大。而对于《中庸章句》本身的分段,陈荣开未采用以往的“四大支”“三大段”“四大段落”等分法,而是采用了五段式分法:首章和尾章各自成一段,第二至第十一章(共十章)为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章(共九章)为第三段,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共十章)为第四段。在《朱子〈中庸〉结构说(上)》中,陈荣开分析了第一、第二段。对于第一段,陈荣开以图表一帧,指示结构,纵分纲领、中、和,横分性与道、教、效,并按类相从地详细引述了《中庸》经文和朱子所加的注,既而指出第一大段纲举目张地指示了性、道、教三个基本范畴的内在联系,中、和的分别是道的体、用,致中、致和分别是涵养、省察的要诀和达致天地位、万物育的基本功夫。对于第二段,陈荣开也以图表一一显示其内在结构,继而按章节分析其内在关联:第二章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原因,第三章指出中庸之为至德久为民所鲜能的事实,第四章根据这一事实剖析道不行和道不明的原因,第五章和第七章分别带出道不明与不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第六章和第八章分别以舜和颜渊为例,说明道之得行、得明的依凭所在,亦即知、仁这两个造道成德之法。第九章以子路之勇为例,指出知、仁若不纯熟,则不可能达到中庸,呼应了第三章中中庸民所鲜能的事实,第十、第十一章以强勇为主题,分别侧重于勇的程度适中的必要性及勇之所发的恰当性。
在专注于朱子学的学术研究之外,又有对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综述,如,台湾的林庆彰著有《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1992),吴展良著有《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2007),展现了21世纪国内外朱子学研究的丰厚成果。
附注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②同上。
①《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上》。
①《元史·刘因传》。
②《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
②同上。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同上书,第57页。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7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①陈荣捷:《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丁为祥:《如何进入朱子的思想世界——朱子哲学视野的发生学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8页。
①陆敏珍、何俊:《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自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③同上书,第8—9页。
①陈荣捷:《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①张岱年:《福建朱子学》序,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①叶再荣:《福建朱子学一书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8期。
②陈元晖:《闽学源流》序,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③所谓“当代新儒家”共有三代谱系。第一代可以追溯至“五四”时期的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等先驱人物;第二代是指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移居港台的儒家学者而言;第三代则由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等唐、牟的学生组成。
①钱穆和劳思光并不能算作当代新儒家。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先生曾撰文《钱穆与新儒家》,析别钱穆与新儒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钱穆拒绝以西方哲学来诠释和契接儒学。而张丰乾先生也指出,钱穆的视野是打通经学、子学而贯穿中国通史的,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意义绝不是“当代新儒家”这一名号可以涵盖的。而就劳思光先生来说,他本人并不以新儒家自居,主要原因在于他并不认同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构想,认为传统的天道论、本性论以至当代的道德形上学,都会偏离传统的心性工夫论的正路,使儒学强调的“主体性”无法确立。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①罗义俊:《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读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心体与性体·附录》,第515页。
①参见《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②《二先生语》二上。
③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序》,第2页。
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①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②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序》,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2页。
③同上书,第3页。
①黄俊杰:《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3—112页。
②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继起争议》,载黄俊杰《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59—211页。
③劳悦强:《从〈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论朱熹的诠释学》,载刘笑敢《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85页。
④刘述先:《“朱熹对(四书)与〈易经〉的诠释”重探》。见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第76—87页。
⑤白奚:《二程与朱子对“仁”的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载黄俊杰《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37—259页。
① Kim Chong Chong and Yuli Liu(eds.),Conceptions ofVirtue:EastandWest.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2006.
②Dao,Vol.V,2005.
③ On-cho Ng(ed.),TheImperative ofUnderstanding:Chinese Philosophy,Comparative Phi-losophy,and Onto-Hermeneutics,New York: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2008:261-272.
④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 37.4,2010:639-654.
⑤ 收录于John Makeham(ed.),Dao Companion toNeo-Confucian 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Verlag,2010:177-195.
⑥ 收录于即将出版的David Jones&He Jinli(eds.),Rethinking ZhuXi:Emerging Patternswithin the Supreme Polarit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⑦ 收录于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ew Series,40.2,2010.
①参见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②李明辉、叶海烟、郑宗义合编:《儒学、文化与宗教——刘述先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版。
③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68页。
④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2009年第5期,第151—184页。
⑤《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624页。
⑥《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32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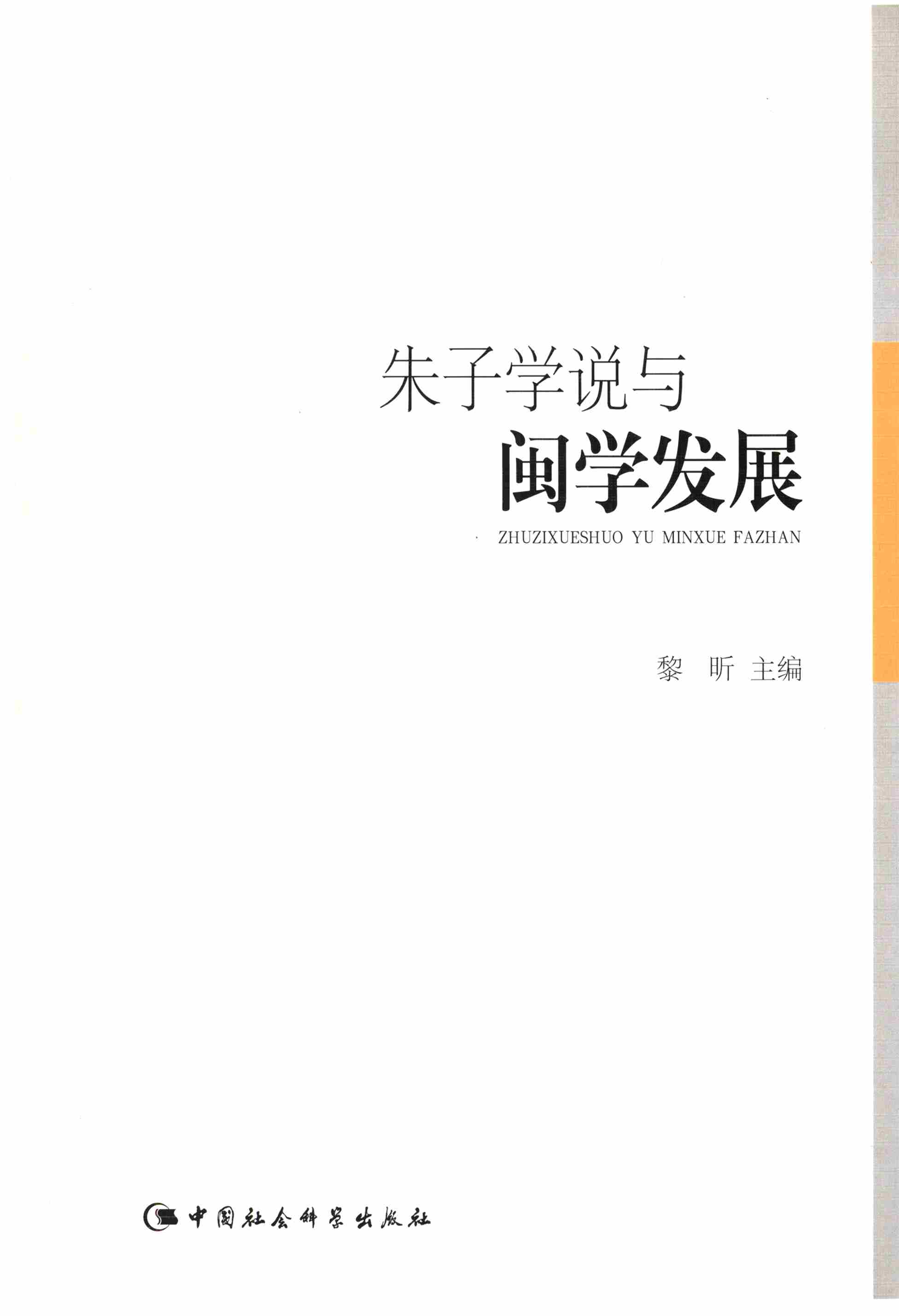
《朱子学说与闽学发展》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八章,主要包括福建历史文化发展与闽学的产生、朱子学说与闽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传承、朱子学说与闽学思想的基本内核、朱子学说与闽学的社会教化论、朱子学说与闽学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等内容。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