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344 |
| 颗粒名称: | 绪论 |
| 页数: | 43 |
| 页码: | 1-43 |
内容
朱子哲学重本体,也重工夫,但心性论思想最终要在工夫修养中落实,所以工夫论在朱子哲学中又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涵养与致知是朱子对二程基本工夫路径的继承,经由朱子成为宋明理学两大工夫路径,在朱子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朱子的出现“使得理学中的理性主义占了主导地位,这是他对民族精神不可低估的影响,了解这一点才能认识朱熹哲学的由来和意义”①。涵养工夫作为朱子工夫论的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涵养在朱子工夫论中处于什么地位?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如何?涵养工夫在晚年是否真的出现新的变化?朱子涵养工夫变化的阶段为何?其变化背后的理据何在?如此诸多问题则仍在学界研究视野之外。再者,历史上有诸多关于朱陆异同的争论,其中对朱子涵养工夫的争论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其中认为朱子涵养工夫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的观点更多地被放在朱陆异同的视域当中去讨论,极少有人去考察朱子本身的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这是以往考察朱子涵养工夫思想的局限性。王阳明曾作《朱子晚年定论》,其引朱子关于涵养思想的三十多封书信,以此作为“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并不能真正定论朱子的涵养工夫思想,但是由于阳明及王学后人对朱子的判定在舆论上造成很大影响,反而引发历史上更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或是朱陆晚年异同之争,或是朱王异同之争,诸多争论甚至延续到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当代学界,其中不能绕开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讨论。所以,如果要对历史上关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争论有较彻底的解决,就应该回到朱子本身对涵养的论述中去寻找答案。对朱子涵养工夫做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进行脉络化的梳理,首先要对朱子一生的思想做脉络化的考察,大体分出朱子思想的重大转折点和发展阶段,不仅关系到对朱子涵养工夫的正确理解,更关系到对朱子思想观点的最终判定。
第一节 研究意义
涵养工夫是朱子工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子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学界却缺少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脉络化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晚年阶段的工夫思想没有特别的注意,这说明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历史上对朱子涵养工夫认识的论争始于朱陆异同之争,“朱陆晚同”论者希望以朱子晚年的涵养思想为依据,试图“合同朱陆”,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也似乎有此意图,如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朱陆晚年同异”“朱子晚年定论”等相关问题的大量争论,其中朱子涵养工夫也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不仅是朱子工夫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人对朱子思想判定的主要依据。所以,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全面、客观的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脉络化的梳理不仅可以厘清历史上对朱子晚年涵养工夫观点的得失,更直接关系到对朱子哲学的正确理解。
一 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需要深入
朱子重本体,更重工夫,但朱子思想的落实最终是在工夫论上。朱子工夫论的基本架构是继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大工夫进路而来,涵养与致知被称为朱子工夫“翼之两轮”,可见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方法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具体居于什么位置,其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则需要进一步追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涵养与致知是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就确立的两个基本为学进路,又因鹅湖之辩是朱陆二人围绕“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展开的,所以学界认识朱子涵养工夫的地位也多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入手。缺少对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的关注。但是不能否认,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涵养工夫内部之间的关系都是定位涵养工夫在整个工夫论中的地位的重要参照,而这需要做专门的梳理与考察。并且,根据历史上提出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发生了转向,是否真的有变化,如何变化也是需要专门解决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脉络化的梳理才能知晓,同时还要对朱子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做脉络化梳理才能知晓。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思想的研究对以上问题并没有十分重视,对朱子涵养工夫研究的结论多停留于“中和新说”阶段,缺少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进一步探讨的兴趣与意识。以中国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他也认为:“(朱子)40岁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为定论。”①若以牟先生此观点为据,显然没有讨论朱子40岁后涵养工夫的必要,但如此则无法解决学界的诸多争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认识也是不够完整的。因此,要了解朱子涵养工夫的全貌不仅要对“中和新说”之后朱子涵养工夫的思想发展做动态考察以完整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的整体脉络,还要重视朱子40岁之后特别是晚年时期涵养思想的最终结论。也就是说,要全面了解朱子的工夫论,朱子涵养工夫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要对朱子涵养工夫有全面的把握,就应该重视对朱子涵养思想的脉络梳理,特别重视“中和新说”至朱子晚年涵养思想发展的整个脉络,同时也要系统地、动态地考察朱子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如此才能对朱子涵养工夫有较为完整的、准确的把握。
二 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认识存在误区
学术史上对朱子涵养工夫的争论主要是在朱陆之辩的视域之中进行的,由于朱陆鹅湖之辩的主题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故涵养和致知的关系也成为后人对“朱陆异同”判断的核心内容。对于“朱陆异同”,学界有观点认为象山重“尊德性”而朱子是“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亦有观点认为朱子重“道问学”,轻“尊德性”;较多观点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本,象山以“尊德性”为本;有学者甚至直言:“朱熹是以‘道问学为主’的理学宗旨,陆九渊是以‘尊德性为宗’的心学宗旨。”①无论观点是非对错,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固然是判定“朱陆异同”的重要标准,但是不能把“朱陆异同”的认识局限在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之中,更不能把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异同局限在二者关系的异同,还要回到对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各自工夫本身的异同做进一步的追问。由此,学术史上对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认识就曾出现一种误解,即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没有什么区别,涵养工夫本身不是“朱陆异同”的分歧。这就容易给“朱陆异同”的判断制造一个认识的误区:如果朱子重涵养,则可与象山归同;如果朱子重穷理,则与象山为异。如此,虽然“朱陆异同”的争论延续至今,但争论的焦点更多地还是集中在朱陆之辩的学术事实以及二者“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对比上,最后忽略了对二者涵养工夫异同的注意。这种认识的误区最后直接体现为后世在“朱陆异同”的论争中出现以涵养工夫弥合朱陆的观点,其中以陆王一系提出的“朱陆晚同说”最为典型。“朱陆晚同说”认为朱子在晚年改变了之前的立场,认为“尊德性”重于“道问学”,故折从象山。陆王一系以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判定“朱陆晚同”,与持“朱陆晚异”观点的朱子一系的学者相对峙,持续了很长的论争,甚至最终陷入朱陆、朱王的门派之见中,最终也并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本身有一个客观的、系统的结论,反而加深了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误解。
三 对朱子涵养工夫脉络的判断存在争论
学术史上朱子对涵养工夫脉络的判断出现争论缘于“朱陆异同”之争,陆王一系学者通过对朱子涵养工夫做部分动态的考察,做出了“朱陆晚同”的判定,试图以此来合同朱陆,由此引发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明代程敏政是最早明确提出“朱陆晚同说”的学者,他认为朱子晚年以“尊德性”为重,并认识到自己“道问学”的支离之病。他说:“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见于书者可考也。……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语,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见于义跋;又屡有见于支离之弊,而盛称其为己之功。”①后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虽然阳明并未交代其作《朱子晚年定论》是为了证明“朱陆晚同”的立场,但其在序中说:“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②而《朱子晚年定论》摘录朱子的三十四封书信大多是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内容③,这在当时“朱陆晚年异同”论争的背景下很自然地被列入“朱陆晚同说”的立场,被认为是对程敏政的接续。对此,同时代的学者陈建便说:“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子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卷正相相唱和矣。”①由于阳明及王门后学的学术影响力,《朱子晚年定论》对后人认识朱子涵养工夫以及朱陆异同等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朱子晚年定论》并没有对朱子“晚年”做时间上的说明,对其所引用的书信也没有进行考证和说明,并且对朱子书信的引用还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②,阳明此做法随即引发了罗整庵、陈建等朱子学者的批判,陈建便说:“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③其认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狂误后学之深”④。与陆王学者相对,陈建提出“朱陆早同晚异说”。陈建说:“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殁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⑤他认为:“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⑥可见,陈建认为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是不同的。陈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引起了王门的反对,此后关于朱陆涵养问题的争论则演变为朱王门见论争,二者偏执一方。《四库提要》就指出:“朱陆两派,在宋已分,洎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申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所好。”①但是,朱子晚年涵养工夫本身的真面目却在争论的焦点之外,最终也没有呈现关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真实面貌。
至清代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亦是王学立场,其作《朱子晚年全论》就是为了支持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李绂认为阳明所引朱子书信太少,所以引用了朱子三百多条的书信来证明朱子晚年涵养重于“道问学”,与象山为同。他说:“今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共为一编。”②从内容上看其实是《朱子晚年定论》的扩充版,核心内容仍是朱子涵养工夫,并最终将朱子晚年涵养思想归同于象山。他说:“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则符节相合。”③又说:“陆子主孟子‘先立乎大,求其放心之旨’,则未发之时无不涵养矣。涵养于未发之前,盖延平教朱子之法,而朱子后来弃而不用,晚年始复追寻,有‘孤负此老’之悔。”④又说:“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朱子晚年定论》,陆子既不及闻其说。”⑤但是李绂之说并非完全属实,其所引朱子书信并不是皆在朱子51岁以后,其引朱子《答潘叔度》五书中,书一、书二是在1173年,书三、书四在1174年,书五在1186年,分别为朱子44岁、45岁、57岁,并非都在51岁后。①也并没有真正做到“晚年论学之书,则片纸不遗”②。为了反驳王阳明与李绂,朱子学者王懋竑为此重新校定《朱子年谱》四卷,并作《年谱考异》,“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说”③。然而王懋竑虽然将朱陆之辩的过程考证得十分详细,但并没有正面回应阳明和李绂对朱子晚年涵养思想的判定问题。中华民国学者钱穆先生、现代学者如陈荣捷先生、陈来先生等亦有大量讨论朱陆晚年异同以及《朱子晚年定论》的评判问题,钱穆说:“淳熙十五年与象山争《太极图说》,书问往返,传播远近,而后两人异同之裂痕,遂暴露无遗。其时朱子年已五十九,上距鹅湖初会,先后已历十有四年。此下又四年而象山卒世,又八年而朱子亦没。在此一段时间之内,朱子思想体系进而益密,其学问规模亦廓而益大,然犹是与二陆鹅湖初会时之规辙,而日臻于平实圆通,非有如阳明所谓‘晚年定论’之说也。”④陈荣捷后来总结前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主要有四点:“一为其误以中年之书为晚年所缮;二为其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三为其断章取义,只取其厌烦就约之语与己见符合者;四为其误解‘定本’,且改为‘旧本’。”⑤陈来说:“王阳明之《晚年定论》不顾材料考证,徒据臆想(要其意亦不在考证也),以‘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其实《大学》《中庸》的章句或问皆成于朱熹60岁。而《晚年定论》收书三十二通,其中答何叔京等十一通皆在50岁以前。”①以上朱子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回答了朱陆晚同的立场,却几乎没有从朱子涵养工夫本身的脉络发展上回应历史上对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判定,目前学界对朱子的研究也没有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从确立至晚年的脉络发展状况,所以至今也无法对朱子涵养思想的早晚变化做出判定,最终解决以往的争论。为了解决如上问题,必须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脉络发展做完整的研究。
四 对朱子涵养工夫优劣的判定有待商榷
学术史上对朱子思想的研究至中华民国时期出现一个较大的转向,即对朱子的研究重点从工夫论走向心性论,乃至宇宙观,并最终由此对朱子思想做出优劣的判定。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华港台新儒家多持“尊陆贬朱”的立场,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朱子的涵养工夫劣于象山的涵养工夫,最终延伸到思想系统的优劣。牟宗三说:“心之仁不待仁外之敬以求之也,仁体即敬也。此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创生直贯义,非心、仁、敬三者之关联义也。由此关联义而见其为静涵静摄系统,而非创生直贯之纵贯系统也。”②牟宗三认为朱子与象山之区别在于“横贯”与“纵贯”系统的本质不同,朱子属于“静涵静摄系统”,朱子的涵养工夫是好习惯的养成,非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他说:“若如朱子所论,只于空头的察识外,知尚有未发时,故复补之以空头的涵养,此虽亦可得力,然所养成者只是不自觉的好习惯,以此为本只是外部的空头涵养工夫之为本,非内部的性体本心之实体自身之为本也。”③如此,牟宗三最终将朱子的涵养工夫判定为外在的道德实践的养成,也就是说是被约束和训练而成的德行,而非心内自觉的道德实践,他说:“然此尊德性显然是经验地、外在地。推之,其一切敬的工夫亦都是经验的、外在的。以朱子持身之谨,克制之严,自是尊德性,然是经验地尊、外在地尊,故乏自然充沛之象。”①最终,对朱子的涵养工夫做了经验的、外在的判定。
基于这样的理解,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工夫属于小学工夫,不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而是通过习惯和练习完成的,他说:“朱子以小学教育即为‘做涵养底工夫’,此即为空头的涵养。此是混教育程序与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工夫而为一,而不知其有别也。……即‘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亦仍是不自觉的自然生长,还仍不是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事。”②又说:“其所意谓之涵养只是一种庄敬涵养所成之好习惯,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养习,只是类比于小学之教育程序,而于本体则不能有所决定,此其所以为空头也。”③最终以“空头涵养”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出价值判断。牟宗三基于这样的判定,他认为朱子的涵养并非承于孟子正统,最终对朱子做了“别子为宗”的判定,他说:“是以朱子如此讲空头的涵养以遮‘先识端倪’之本体论的体证,实是混习惯与自觉为一。此皆非孔子讲仁、曾子讲守约战兢、孟子讲本心、《大学》讲诚意、《中庸》讲慎独、致中和之本意。……朱子如此讲涵养显然不够。”④以至于最终,牟宗三对朱子的整个道德体系都做出了“歧出”的判定,他说:“其本体论的体证(体悟)所体证体悟之太极却只成致知格物之观解的,此非延平之静坐以验未发气象之路也,亦非明道‘须先识仁’、五峰‘先识仁体之体’之本体论的体证也,此其所以为歧出也,此其所以终于为他律道德之本质系统,而非自律道德之方向系统,所以终于为静涵静摄系统,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而非本体宇宙论的、即活动即存有的实体之创生直贯义之纵贯系统也。”①综上分析可知,牟宗三判定朱子道德系统为“他律道德”“歧出”“别子为宗”等,这都与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判定是直接相关的。
牟宗三对朱子涵养乃至整个道德系统的判定在学界有很大影响,也影响到后世学者对朱子涵养思想甚至思想系统的判定,现今许多中国港台一系学者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定仍从牟宗三先生之说②,大陆学者亦有此种说法。可以说以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判定是继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定论”,但是此种观点是牟先生自己的创说,是否合乎朱子涵养工夫的本义,实在是有必要做进一步商榷,学界至今对牟宗三判朱子涵养工夫为“他律”之说的也少有回应。要解决以上问题,都需要从朱子涵养工夫本身入手,并对朱子涵养工夫与心性论的关系、涵养工夫与气禀的关系、涵养在其他工夫中的地位等做客观的、全面的梳理才能得知。
第二节 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与不足
总结目前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重视程度和研究程度都远远不够,虽然有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陈来等著名朱子学者在论著中做过专门的讨论,但总体上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论文期刊数量甚至不过百数,这显然与朱子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符,更与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不符。
一 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研究
(一)集中在“中和新说”阶段
学界对涵养工夫脉络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朱子“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时期,对朱子涵养工夫确立后的脉络的发展,特别是对朱子晚年阶段涵养工夫的研究十分缺乏。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下)第三章“中和新说下之浸润与议论”整章探讨朱子“中和新说”后的涵养工夫,他提出朱子“中和新说”涵养工夫就是定论,他说:“新说关于浸润与议论中提出关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之定论。”①其后所附《朱子语类》中的论证材料从朱子41岁开始②,但牟宗三对其所引材料没有进行时间上早晚的区别,说明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脉络发展没有特别关注。钱穆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注意到朱子晚年言敬的变化,他说:“朱子于北宋理学诸儒所言心地修养工夫,其纠弹尤多于阐发处。其为儒释分疆划界,使理学一归于儒学之正统,朱子在此方面之贡献,至为硕大。即二程所言,朱子亦复时有匡正。如言敬,朱子则言不可专靠一边。而朱子晚年,则颇似有另标新说,取以代程门言敬之地位者。此层在朱子并未明白直说,要之似不可谓无此倾向。”③可见,钱穆认为朱子晚年言敬与二程有区别,但他的讨论停留于此,并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讨论。唐君毅的朱子学研究花费大量笔墨探讨朱子的涵养工夫,其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附《原德性工夫:朱陆异同探源》上、中、下三编对朱陆涵养工夫的异同做了专题研究④,但唐先生也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有特别的注意。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也花费大量笔墨讨论朱子的涵养工夫①,但也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有专门的注意。
亦有学者注意到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变化,比如曾亦在《宋明理学》中就提出朱子在“中和新说”中认为“未发时未必为中,已发时未必为和,故欲使未发之中,即在未发时加一段功夫,即涵养工夫”②。他在这里加一个注:“朱子此时尚仅强调未发时一段涵养工夫,以为如此则自能使已发之和,后来方觉得已发时之省察工夫亦不可缺。主敬与致知、涵养与省察须互相发,方能无病。”③这说明其发现朱子涵养工夫是有变化的,但却未能对“后来”做时间上的追问与进一步的分析说明。另有陈林在《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一文中提出朱子晚年对已发未发有重新认识,他说:“朱子晚年试图打通涵养主敬与格物穷理两工夫,强调涵养主敬与格物穷理相互渗透、相互发明,在晚年的朱子看来,未发时固然要做存养工夫,已发时亦要做存养工夫,已发时固然要做省察工夫,未发时亦要做省察工夫,要做到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④此观点之是非暂且不论,但此篇论文却是少有的明确以朱子晚年思想作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体现了对朱子涵养工夫在晚年的发展的注意。
(二)对晚年阶段的研究不足
朱子晚年阶段是朱子人生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不加以关注和研究,亦不可能完整了解朱子思想。朱子晚年又是朱子人生阶段的最后时期,可以说,朱子晚年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和判定是朱子思想最后的定论。朱子晚年对某些观点和问题的阐述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反而恰恰代表了朱子一生当中最关切的问题,也是朱子历经一生思考的问题。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来看,哲学家后期的思想往往会呈现更加严密化的特点,注意力往往不再集中于建构新的思想体系,而更加注重对自身思想体系的修建和反思,这亦是朱子思想不断深化的体现。朱子在晚年时期形成的观点其实是朱子思想中最成熟、最可信的阶段,是朱子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但目前学界对朱子晚年阶段的研究却十分不足,对朱子晚年阶段相关思想都缺乏专题研究,没有相关专著,也没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虽有研究朱子学的大家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陈荣捷、陈来等在论著中对“朱子晚年”的相关思想做部分讨论,以朱子晚年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只搜索到约四十四篇,其中直接关系到朱子晚年阶段研究的不到十篇。以上对朱子晚年的研究皆未涉及涵养工夫这一主题,对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只涉及边缘,可以说学界对朱子晚年阶段涵养工夫的专门研究严重不足,缺乏对朱子晚年阶段的涵养工夫思想的代表性观点,这也成为完整认识朱子思想的困难所在。另一方面,由于前人对“朱子晚年”的时间界定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导致现今学界对“朱子晚年”的认识比较模糊,对朱子晚年阶段的研究也十分不严谨,这也是对朱子晚年阶段涵养工夫做专门研究的困难所在。
总结以“朱子晚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大多对“朱子晚年”未做时间上的明确说明,对引用的材料没有进行考证或说明,自然认定为“朱子晚年”。如在《朱陆晚年之异初探》①中所引“朱子晚年”材料是《语类》中“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②一段,由于《语类》中没有注明由谁所录,但笔者也未对其做时间上的证明。其引《朱子语录》中“江西便有这个议论”一段,由甘节录,时间为朱子64岁后①,作者也未进行说明;另引《语类》中“陆子静之学”一段,由贺孙所录,时间为朱子62岁之后②,作者亦未进行说明。可见,作者虽以“朱陆晚年”为研究主题,却并没有对朱子晚年、陆九渊晚年的时间做清晰的界定或者明确的说明。又如在《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③一文中,作者以“朱子晚年”为主题,但在文中没有任何对“朱子晚年”的时间上的说明,更未对所引材料进行考证,对笔者所说的“朱子晚年”无法知晓。所以,对于“朱子晚年”的研究需要以更为严谨的为学方法对朱子人生阶段和思想阶段做一个相对合理的划分,并对引用的相关文献做时间上的辨析和说明,这也是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脉络化研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及地位研究
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系统中的地位应当是研究朱子涵养工夫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地位的认识主要围绕早期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以及朱陆之辩中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考察。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朱陆之辩的主题,故更偏重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考察,因为持敬是涵养的主要工夫,所以对持敬与穷理的关系,学界研究已经比较透彻,结论比较清楚,存在争议较少,故研究成果本书不再列举。但对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学界的争论比较大。除此之外,由于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关注点都在持敬上,对其他的涵养工夫以及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较少,存疑较多。本书总结了学界对朱子诚意与致知、持敬与克己以及持敬与立志三个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一)诚意与致知的关系
1.朱子重致知轻诚意
以牟宗三为代表,他提出朱子诚意是外在的诚、他律的诚,这与他认为朱子的涵养是好习惯的养成而非自觉的道德实践的判断是一脉相承的。牟宗三认为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是“以知言诚”,认为这是朱子诚意工夫的局限,他说:“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粘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之,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①可见,牟宗三认为朱子的致知吞没诚意,朱子偏重致知一方。他又说:“但以此‘真知’说诚意,反过来亦可以说诚意只是知之诚。是则‘真知’与‘诚意’只是一事之二名,意之诚为知所限,而与知为同一。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②由此,牟宗三认为朱子的诚意只是知的落实,而不是行的落实。
牟宗三又进一步说:“是即不得不承认‘意之诚’与‘知之真’为两回事。即是意之诚不与知之真为同一,朱子亦可让意之诚有独立之意义,然而知之机能与行之机能,在泛认知主义之格物论中,只是外在地相关联、他律地相关联,而行动之源并未开发出,却是以知之源来决定行动者,故行动既是他律,亦是勉强,而道德行动力即减弱,此非孟子说‘沛然莫之能于能御’之义也。”③由此,牟先生对朱子做出了“知行不一”的判断,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是“道德无力”。这就是为何牟宗三批评朱子的涵养是“空头涵养”,察识也是“空头察识”的原因,他认为二者都不是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他说:“涵养既空头,则察识亦成空头的。其着力而得力处只在‘心静理明’。涵养的心静故理明。……或在格物穷理处能逐步渗透或静摄那存有之理。此即成全部向外转……此种察识只能决定(静摄地决定)客观的存有之理,而不能决定吾人内部之本心性体。其涵养所决定的,是心气质清明,并无一种超越之体证。其察识所决定的,是看情变之发是否是清明心气之表现,亦非是看本心性体之是否显现。”①
2.朱子重诚意
钱穆与牟宗三不同,钱穆在《朱子新学案》第2册中又专门讨论了“朱子论涵养与省察”②,钱穆认为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朱子工夫论的严密性,他说:“朱子自所主张欠了分数为自欺之根之说,虽非《大学》文本之意,而节去之终为可惜,乃移置于此。……然朱子之说,终始本末一以贯之,兼顾并到,互发互足,则遥为细密而圆满,可遵而无病。有志之士所当明辨审择也。”③钱穆认识到朱子对诚意思想的重视,也对朱子晚年修改诚意的工作做了肯定,他说:“朱子易箦前三日改此‘一于善’三字为‘必自慊’三字,乃与下文注语言‘诚意者自修之首’一句义指相足,工夫始无渗漏。此其用意,可谓精到之至。……是岂单标孤义,杜塞旁门,所谓易简工夫之所能相比拟乎?”④显然,钱穆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工夫,甚至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优于象山之易简工夫。
陈来提出朱子晚年仍持“致知在诚意之先”的立场,并且陈来提出这是朱子晚年与象山的区别,他说:“朱熹晚年,陆九渊死后,陆氏门人包显道率人至闽来学,朱熹一见面就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如某便谓须当先知得方始行得。’这里朱熹认为陆氏本意未尝不教人作圣贤,但不读书穷理,无法了解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这样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①可见陈来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思想,并认为这是朱子优于象山的地方,他说:“朱熹后来意识到,关于气质对人的意识的影响,由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不能自发地达到道德完善(意不能在自诚),以及必须通过长久的认识和磨炼才能去除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些方面才是陆学失误真正重要的问题。”②陈来进一步提出,象山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而朱子在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后更强调做工夫的重要性,这是朱子思想的进步之处。
针对牟宗三对朱子的诚意是“知而不行”的判断,方旭东认为西方哲学在处理“知而不行”问题时,或强调认知,或强调意愿/意志,或归结于非理性自我,而在程朱(尤其是朱熹)这里,这些思考以一种综合的面貌呈现,他认为朱子“知而不行”的“知”只是一种“浅知”,不是“真知”,“真知”之“真”是从“知”的效果上讲的,强调“真切不虚”。这种“真知”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亲身实践的亲知,求知或致知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道”或“见理”的道德践履。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③方旭东显然注意到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注意到朱子的诚意工夫是要贯通知行。
(二)持敬与克己复礼的关系
“克己复礼”来自《论语·颜渊》中的一段,是孔子训示颜回如何为仁的方法,颜回在孔门中地位很高,克己复礼思想得到后世学者推崇。朱子和象山皆言克己的重要,朱子在《仁说》中就提出了克己工夫,象山言“义利之辨”也重克己工夫。历史上亦有持“朱陆晚同”观点的学者以克己工夫合同朱陆,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然朱子晚年,乃有见于学者支离之弊……而陆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之语,见于奠东莱之文。……或乃谓朱陆终身不能相一,岂惟不知象山又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诚。”①钱穆则认为朱陆二人对克己工夫的态度不同,其以《语类》中朱子与陆子寿论“克己复礼”②指出:“朱子主张教人克己复礼,谓众人皆有此病,须克之乃可进。二陆兄弟主张心即理,不喜言克己,故复斋以此归朱子,而朱子以此答之。但尚未辨到克己复礼工夫是一是二。”③钱穆又说:“朱子晚年好提克己工夫,然恐不仅为象山一派所不喜,即一般学者,殆亦多抱颜子地位何待克己之疑。”④可见,钱穆认朱子晚年更重克己,而陆学则不喜克己,这是朱陆言克己的分歧。
钱穆还注意到朱子言克己与敬的关系的变化,他说:“朱子提出《论语》孔子告颜渊以克己,以为求仁之要,一言而举,此意当在其辨已发未发而提出程门敬字之后。”⑤钱穆认为朱子提出克己在提出主敬之后,克己工夫的提出改变了朱子本来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两大工夫架构,他说:“于伊川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项外,特增入克己一项,几于如鼎足有三。”⑥钱穆还提出朱子言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出现了三变,他说:“伊川以《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此注乃以《论语》孔子告颜渊问仁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显已把孔门心法转移了地位。伊川又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先亦引其说,稍后则谓敬之外亦须兼用克己工夫,更后乃谓克己工夫尚在主敬工夫之上。关于此,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①钱穆后来又在《朱子新学案》中详细分析了朱子言克己的变化,他认为朱子46岁时对于克己工夫的认识是:“克己、复礼分作两项说,又谓克去己私了,正好着精细工夫,则克己工夫只是初步。……殆此时朱子仍遵程说也。”②钱穆提出:“朱子五十以后……以克己与敬与致知并列为三,而必先言伊川所以只言涵养不言克己之意,然后始言涵养克己亦可各作一事。”③他说:“朱子年六十以后,乃始于克己工夫表出其十分重视之意。”④又说:“及其年过六十,乃始明白以克己工夫放在持敬工夫之上。”⑤可见,钱穆认为朱子越来越重视克己,认为朱子60岁后对克己工夫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持敬,最后钱穆提出朱子改变了以涵养和致知为两个工夫架构,并以克己为第一等工夫,他说:“伊川所谓敬义夹持,涵养致知须分途并进,其实也还落在第二等。须如朱子所发挥颜子克己工夫,乃始有当于圣门为学之第一等工夫。”⑥可见,钱穆认为朱子对克己的重视已超过了持敬,由于学界对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关注得不多,钱穆的观点没有引起很多讨论,但朱子晚年后的工夫架构是否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需要对朱子论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做脉络化的梳理才可知晓。
(三)持敬与立志的关系
对于朱子立志工夫的研究,学界关注得十分少,但钱穆对朱子立志工夫有较早的注意,他认为:“朱子特拈立志一项,已在晚年。朱子立志的工夫是为了补居敬工夫之缺”①可见,钱穆认为朱子晚年时提出立志工夫是为了补充持敬工夫的不足。钱穆认为朱子晚年提出立志工夫是其晚年工夫思想更加通达的体现,他说:“此谓闲时不吃紧理会,不仅陆学轻视学问有此弊,即专务居敬,不兼穷理,亦必有此病。而朱子尽把来归在不曾立志上,此见朱子晚年思想之力趋简易而又更达会通处。”②可见,钱穆认为象山工夫之缺在于专务居敬,没有兼顾穷理,而朱子晚年把成德失败归于立志工夫,这是朱子晚年思想简易又通达的表现。钱穆又说:“徒尚立志,不务向学,诚是偏颇。然徒知庄敬持养,而不重立志,亦是有病。故朱子教人相资为益。后人徒言程朱言居敬,此皆未细读朱子书,故不知朱子晚年思想之不断有改进处。”③钱穆认为朱子晚年重立志,是二程言敬与象山言立志的结合,是晚年工夫思想严密的体现,而这与朱子晚年的心性论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他说:“朱子晚年又论志与意之分别,提出意属私,故须诚意,志则能立便得,更无有立伪志者。理学家中,惟朱子最善言心……惟朱子言心学工夫,最于理学家中为细密而周到,细看上列诸章自见。”④由此可见,钱穆从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的重视看到朱子晚年心性论的完善,从而认为朱子言心学工夫最为严密,对朱子晚年言立志工夫做了肯定。
在此基础上,钱穆又对朱陆二人言立志工夫做了对比,钱穆认为虽然朱子言立志有承袭象山的部分,但朱陆二人的立志工夫有本质的不同,他说:“象山教人立志,朱子晚年亦教人立志,此见朱子肯兼取陆学之长。但陆学只言立志,不言学,故朱子特举五峰说以救其弊。此见朱子之博采,亦见朱子立言,必斟酌而达于尽善之境。”⑤钱穆认为朱子晚年言立志是朱子取陆学之长的体现,但陆学言立志有弊即在于只言立志,不言“道问学”,所以朱子取五峰之说,将立志与问学相互补充,这是朱子晚年工夫思想完善的体现。但是钱穆强调朱子晚年虽重立志但不是转从陆学,他说:“是朱子晚年虽履告学者以立志,终不得谓是转从陆学。”①钱穆对朱陆二人言立志工夫做了区别,他说:“象山教人立志,似只重当下行处。朱子谓人不立志则不肯闲时吃紧理会,则偏重知一边说。此两家同言立志而意趣有别也。”②可以看出,钱穆认为陆学言立志偏向行,朱子言立志偏向知,这是二者言立志的区别,是否如此也要对朱子立志工夫做细致的梳理才可知晓。唐君毅亦注意到朱陆二人言立志的不同,他认为朱子对立志的重视不如象山,他说:“朱子晚年又尝谓:‘从前朋友来此,某将谓不远千里而来,须知个趣向,只是随分为他说个为学大概。看来都不得力。今日思之,学者须以立志为本。’然只以趣向为志,似不够分量。观朱子于五峰所谓‘志立乎事物之表’之一义,亦实未能如象山之重视。”③唐君毅认为朱子虽然重视立志,但只是立乎事物之表,但重视的程度不如象山。可见钱穆、唐君毅均注意到朱子晚年言立志工夫,但二人对朱子言立志工夫都有不同的评价,至于晚年朱子对立志工夫重视的程度如何,其与持敬的关系如何,二人的判断是否中肯,需要对涵养与立志关系的脉络进行梳理后才可知。
三朱陆涵养工夫异同研究
学界对朱陆异同的判断多是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去讨论,所以学界在对朱陆涵养异同研究中不免要对二者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进行讨论。牟宗三认为朱陆的差异是二者思想系统的不同,他说:“依吾人现在观之,‘陆氏之学与朱子合下不同’此诚然也。但此不同根本是孟子学与《中和新说》之不同。”①牟宗三认为朱陆不同是朱子的“中和新说”与孟子“求放心”思想的根本不同,朱子“中和新说”确立涵养思想,牟宗三意指朱子涵养思想与孟子“求放心”不相契,而象山从孟子,这是朱陆二人涵养不同的原因。牟宗三又从朱子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判定朱子涵养工夫是经验的、外在的道德实践,而象山则是自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他说:“尊德性琐碎委散于道问学之中,全幅心力集中于道问学,而尊德性则徒见其随道问学而委散,而不见其直承天心仁体之提挈,此所以象山观之,并未尊得起。朱子亦觉此病,故认从象山游者,于践履上皆有气象可观,而自己之门人,则虽读了许多典策,却无甚挺拔处。……凡此种道问学中之尊德性,皆是经验的、外在的,惟赖戒慎于风习名教而不敢逾越以维持其尊德性;此是消极地尊,并非积极地尊。盖其主力在知识典策,故其所成亦在此。……是则朱子之途径实是道问学之途径(为学日益),于学术文化自有大贡献,而于成圣成贤之学问(为道日损)则不甚相应也。”②在此,牟宗三明确认为朱子重“道问学”而轻“尊德性”,认为朱子的“尊德性”工夫受到“道问学”的限制而成为“道问学”中的“尊德性”,是经验的、外在的、他律的“尊德性”,不是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所以朱子在“道问学”工夫上有很大贡献,但相比“尊德性”,真正实践工夫就差很多了。在此基础上,牟宗三对朱陆二人的工夫进路做了判定,他说:“朱子与五峰、象山之异,根本是顺取之路与逆觉体证之路之异,并不是笼统地‘自下面做上去’与‘自上面做下来’这单纯的两来往之异,亦不是从散到一与从一到散之异。”③基于牟宗三对朱子“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认识,牟宗三认为朱子的“下学而上达”是“逆觉体证”,象山是“顺取”,象山的成德路径优于朱子。
唐君毅认为朱陆的不同首先在于工夫的不同,而工夫的不同首要是涵养工夫的不同,而二者涵养工夫不同的原因在于二者对心与理关系认识的不同。唐君毅说:“吾人谓朱陆异同之第一义在二贤之工夫论,唯在此工夫论之有此异同,而朱陆乃有互相称许之言,亦不免于相非。至在朱子晚年之言论,如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辑,其非议陆子之言尤多。”①他认为朱子晚年多非陆学,而朱陆不同的第一义在于工夫的不同,这种工夫的不同又首先在于涵养的不同,他说:“其早年鹅湖之会中,于尊德性道问学之间,各有轻重先后之别,不能即说为根本之不同甚明。而朱子与象山在世时讲学终未能相契,其书札往还与告门人之语,或致相斥如异端者,乃在二家之所以言尊德性之工夫之异,随处可证。”②可见,唐君毅认为鹅湖之会时,朱陆二人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各有轻重先后之别,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先、为重,象山以“尊德性”为先、为重,他又认为二者终未能归同的原因在于二者“尊德性”工夫的不同,亦即涵养工夫的不同。唐君毅对朱子的判断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需要进一步证明,但其指出朱陆二人的不同最终归于“尊德性”工夫上,而这种不同又决定了朱陆二人思想系统的不同,这为朱陆异同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唐君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朱陆异同”争论的根源最后都转向心与性理的问题上,他说:“整庵与阳明之宗主不同,然其以朱陆之异在心与性之问题则一。下此以往,凡主程朱者,皆谓陆王之重心,为不知格物穷理而邻于禅。如陈清澜《学蔀通辨》,论朱陆早同晚异,陆学唯重养神,张武承《王学质疑》,亦疑阳明言非实理也。王学之流,则又皆明主心与理一。……则言朱陆之异同,当在此心与性理之问题上措思,固阳明以降宗朱子与宗陆王者共许之义也。”①
唐君毅还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和朱止泉著“朱子未发涵养辨”一章,并认为二者“皆谓朱子之未尝不先尊德性、务涵养而重践履,而合乎陆子”②。唐君毅反对二人以涵养工夫合同朱陆的观点,他说:“今如缘二贤皆重涵养,谓朱陆本无异同,则又将何以解于朱陆在世时论学所以不相契之故?又何以解于后世之宗朱或宗朱陆者,其学风所以不同之故?以此言会通朱陆,抑亦过于轻易。”③唐君毅认为朱陆涵养工夫的不同归根结底在于二者心与理的关系不同,心性论的不同导致工夫上无法合同。他说:“此其义与象山之言工夫,唯在剥落去人心之病障,以自复其本心,而发明其本心,以满心而发之旨,初无大不同;而在与其宇宙论上或泛论工夫时看心之观点,明有不一致处。”④他又认为阳明契于象山心即理之说,而判定朱子“心理为二”是因为他“已知朱陆之异,不在尊德性与否,而在所以尊德性之工夫与对心理之是一是二之根本见解之异同上”⑤。他提出朱陆异同应该从心性论上找原因,他说:“则言朱陆之异同,当在此心与性理之问题上措思,固阳明以降宗朱子与宗陆王者共许之义也。”⑥从唐先生的观点可知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的异同需要到朱陆二人的心性论上去寻找,同样,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离不开朱子的心性论,朱子涵养工夫变化的原因也要回到心性论上去寻找。
钱穆对朱陆涵养工夫的异同有较多研究,他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提出朱陆二人都有未发涵养这一层工夫,他说:“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①可见当时钱穆认为朱陆都有未发涵养工夫,似以二者涵养为同,钱穆又认为清儒对“朱陆异同”的争论都在文字之间考证求索,故没有看到二人之同。后来,钱穆又提出朱陆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不同,他说:“象山可谓能开示学者以为学有本之道,而朱子尤必进之以本末精粗之一贯。两人间所以终不能相悦以解。后人以象山之非朱,遂疑朱子为学,只在博览精考。或疑朱子论学之有本,乃与象山交游后晚年之所悟。则试考之淳熙乙未鹅湖相会以前朱子论学之经过,亦可以见其言之无稽矣。”②可见,钱穆认为象山重“尊德性”,而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一贯,二者不能为同。钱穆提出认为朱子只重“道问学”是因为没有看到朱子的“尊德性”工夫早在鹅湖之会前就已确立,并且对“尊德性”的重视持续至晚年。钱穆说:“乃后之尊朱者,又必谓朱子是时尊德性之学已熟,‘今觉得未是’一语不可泥。在此以前,朱子亦极注意尊德性工夫,常作反省,常自以为未是。及其晚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何尝不可自觉未是。且朱子所自以为未是这,似指其教人方面,重说了道问学,轻说了尊德性。两边相比,不免于若此。其谓未是,却不是要专重尊德性,不重道问学。”③钱穆以颜回赞美孔子的话来形容朱子晚年的工夫境界,这本是朱子称赞颜回的话,朱子说:“颜子穷格克复,既竭吾才,日新不息,于是实见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④他认为朱陆皆重“涵养”,强调朱子对涵养工夫的重视从鹅湖之会前直至晚年,只是朱子在教人时重说了“道问学”,轻说了“尊德性”,才使世人造成了误解。
陈来明确反对以涵养合同朱陆,他认为朱子在己丑后,“确认了心有未发之时和已发之际,强调已发时须省察,未发时更当涵养,以未发涵养为本,敬字贯通动静,这些都说明朱学中本来包含着重视涵养的一面。己丑后至壬辰《仁说》之辩论,朱熹心性哲学的体系已全面形成并日趋成熟,他的心为知觉、心具众理、人心道心说以及主敬穷理、涵养进学的方法的确立使他与稍后的陆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所以,在鹅湖之前朱熹根本不是‘未会而同’,相反,他自己早已走上了一条与陆学完全相反的为学道路,从鹅湖前后开始,他对陆九渊的一切公开反驳,都是他自己的学问主张完全合乎逻辑的一个结果”①。在此,陈来认为朱子在《仁说》后涵养的基本方法和立场与陆学的涵养工夫从根本上出现了区别,所以朱陆涵养工夫是不能为同的。陈来在对朱陆之辩的书信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朱子对象山的攻击是因为发现了二者涵养工夫的不同,他说:“淳煕乙巳后,朱熹不再称陆学持守收敛之功,更多地开始强调其狂妄粗率之病而表示忧虑。”②可见,陈来认为朱子56岁后不再肯定陆学的涵养工夫,反而对其狂妄粗率之病表示忧虑,其转变的原因在于意识到自身与象山涵养工夫的不同。他说:“朱熹不但重视致知进学,也重视涵养本原,即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但朱熹之尊德性与陆学不同,不是专求发明本心,而是取伊川‘涵养须用敬’,强调主敬功夫。在外则庄整齐肃,于视听言动、容貌词气上下工夫;在内侧则主一无适,常切提撕,不令放佚。故从朱熹看,陆门学者专求什么顿悟本心,而把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纳入礼教范围方面却毫无作用,以致‘颠狂粗率尔于日用常行之处不得所安’成为陆门的一个普遍流弊。这一点是朱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注意和考虑过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陆学越来越感到不安,以致最终对陆学转而采取了全面、激烈的批判态度。”①如此可见,陈来认为朱子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并不是偏重“道问学”一方,但他指出朱陆二人“尊德性”的工夫是不同的,象山的涵养是发明本心,朱子则是主敬涵养,以前没有注意到象山涵养工夫的弊端在于专务本心而失去礼法的制约,但在注意到象山涵养工夫没有礼的规范后才对象山采取全面、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此,陈来指出认识到二者涵养工夫的不同是朱子56岁后对陆学激烈批判的原因所在,陈来认为这种不同是朱陆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即否定了“朱陆晚同说”。陈来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其指出了朱陆涵养方法的不同,朱子是主敬涵养,也指出朱子注重礼法的制约,朱子注重礼法的制约必定会影响到他对工夫论的诠释,也体现在朱子涵养工夫的变化之中,这都有待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学界已对朱子涵养工夫的部分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已经提出了一些代表性观点,但由于学者们研究主题的不同,导致研究程度不一、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研究不够全面的情况,如对朱子中年时期涵养工夫的确立有较多的研究,对涵养整个脉络的发展则缺少关注;对涵养和致知的关系有较多的研究,对涵养和其他工夫的关系则较少注意;对心性论和涵养工夫都各有研究,但对二者的关联则较少注意。这都说明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空间很大,研究价值很高。再者,由于几位最具代表性的朱子学者对本专题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涉及人物和思想的优劣判定,所以,可以说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许多结论有待进一步追究和检查。本书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将以时间为线索,对朱子不同阶段关于涵养的主要观点和在工夫论中的地位进行详细梳理,以对朱子涵养工夫有系统的了解。在对工夫论的研究中,以“工夫不离本体”为思想指引,进一步探寻朱子每一时期工夫思想的变化与心性论的关系,将朱子心性论的发展与工夫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勾勒出朱子思想发展的整体样态。与此同时,以朱子在不同时期与湖湘学、浙学、陆学及程门后学等著名学者的交流与论辩为暗线,一方面对朱子在每一时期涵养工夫的特点做理论和现实上的说明,从而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变化进行立体化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从朱子与其他学派学者的思想碰撞中寻找独属于朱子本身的思想特色和价值。
第三节 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
对朱子思想做阶段划分自古有之,如明代学者陈建将朱子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①,李绂不同意陈建,对朱子做了不同的早、中、晚三阶段的划分。②王懋竑将《朱熹年谱》分为四卷,貌似将朱子思想分为四个阶段,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③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分歧,是因为不同思想家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陈建、李绂围绕“朱陆异同”的主题进行划分,而王懋竑则基于其对朱子生平的考证进行划分。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以朱子年岁为参考,结合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将朱子思想发展做四个阶段划分。
一 第一阶段:早年思想(22—39岁)
朱子的早年思想阶段即学者研究朱子的起始阶段,对此前人有不同的说法和界定,如牟宗三论述朱子思想是从其11岁开始①,钱穆则明确将朱子早年界定为“从游延平前”,也就是24岁前。②陈来作《朱子哲学研究》将朱子“早年”界定于其从学“三君子”至李侗卒,即朱子34岁前。③本书将朱子成年后有了相关论述但尚在探讨阶段的阶段称为“早年思想”,本书将此阶段定为朱子22岁至39岁。
对于朱子哲学思想的开端,学界一般以朱子24岁初见李侗为标志。如牟宗三以朱子24岁初见延平为朱子37岁前思想的第一阶段。④陈来亦说:“朱子早年思想演进,以从学李延平为关键,此在年谱皆已指明。”⑤他提出:“24岁赴任同安途中,拜见了杨时二传弟子李侗。在李侗的引导下,他逐步确立了道学的发展方向。”⑥对于朱子思想的起始,除了朱子的学术交往之外,也可以从其最早的著述窥其端倪。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最早的著述是朱子校订《上蔡先生语录》,他说:“于三十岁(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成《上蔡语录》,此为朱子著述之最早者。”⑦然而初会李侗在30岁之前,显然不能成为探讨朱子思想的开端。除专著外,《文集》所载中尚有更早的论述,陈荣捷认为《文集》“由二十四岁(绍兴二十三年葵酉,1153)至易箦前一日致其门人黄干(1152—1221年),一生著述,除专著外,皆备于此”⑧。陈先生认为《文集》中最早的论述从1153年朱子24岁开始,但是没有具体指出朱子最早论述的内容是什么。后据陈来考证朱子《文集》中最早著述从1151年开始有八篇,如《题谢少卿药园二首》①、《晨起对雨二首》②、《残臈》③等,朱子最早通信开始于1155年,当年朱子有书信八封,如《答戴迈》④、《答林峦》⑤等。《语类》最早由杨子直所录,从乾道六年开始,所以《语类》所载皆为朱子41岁及以后。⑥由此看来,朱子思想的开端可从朱子22岁的诗作开始。
朱子从24岁至34岁从学于李侗,1159年(30岁)校订《上蔡语录》⑦,1163年(34岁)编《论语要义》⑧、《论语训蒙口义》⑨、《延平答问》⑩,1164年(35岁)成《困学恐闻》,至37岁“中和旧说”(丙戌之悟)⑪,朱子自述:“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⑫所以可知以朱子37岁前思想为未定之说是比较明确的。对此,牟宗三说:“然在朱子,三十七岁前犹无‘的实见处’”⑬,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前,对于《中庸》《易传》所洞悟之实体、道体,虽亦有一仿佛之影子,对于《孟子》之本心,甚至《论语》之仁,亦似有一仿佛之影子,然契悟不真,用不上力。”①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以前,虽已确定以《中庸》(首章)、《大学》为入路,对于其内容,则大体只是笼统肤谈。其真切用功是在三十七岁以后。”②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37岁)。”③
37岁至40岁是朱子思想的重要转折期,朱子1167年(38岁)与张栻讨论《中庸》未发已发要旨、先察识后涵养等说④,然而很快朱子又推翻了“丙戌之悟”和“先察识之说”,这点从朱子自述中可以看出;1168年,朱子39岁,成《二程遗书》;1169年,朱子40岁,提出“中和新说”(己丑之悟)⑤,他说:“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⑥可见,朱子自己也说其40岁时改变了此前的论说,明代刘洪谟在《朱子文集大全》序中说:“盖朱子四十以前,如《存斋记》、《答何叔京》二书,专说求心见心,是犹驰心之玄妙,未悟天理时语也。”⑦牟宗三也说:“四十岁以前犹未有此‘的实见处’也。”⑧他认为朱子“新说”后才开始确定其思想的基本架构也是依据朱子的《中和旧说序》做出的判断,他说:“至四十岁因与蔡季通问辨,忽然开朗……遂将此‘天命流行之体’拆散而转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①对此,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确立于己丑。”②可见,学界对朱子这一阶段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对于朱子37—40岁的未定之论,牟宗三将其称为朱子“‘中和旧说’的浸润和议论时期”,是对“中和问题”的参究和发展,他说:“在三十七至四十岁之间,朱子对于此‘天命流行之体’,寂感真几,创生之实体,并无真切而相应之契悟,只是仿佛有一个笼统的影像。”③陈来则说:“朱熹早年中和思想曾经有过两次重要演变(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④以上陈述都说明朱子早年未定之说应该包含37—39岁,所以本书亦以“中和新说”为标志,将朱子22—39岁的思想作为朱子思想的早期阶段,也可以叫朱子早年的“未定之说”。在此期间,朱子著述(大部分是书信)约二百六十一篇。⑤
二 第二阶段:中年思想(40—48岁)
对于朱子中年时期的界定,学界也有若干个观点,比如牟宗三认为朱子37岁时已是中年,他说:“人生三十七已进中年,不可谓少。”⑥但牟宗三所说中年是自然生命意义上的中年,本书以朱子40岁“中和新说”后朱子开始确立自身的思想系统,说明朱子进入中年时期的思想阶段。朱子40岁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⑦、《已发未发说》⑧、《答张钦夫书》“诸说例蒙印可”⑨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的确立,“中和新说”代表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中和新说”后朱子确立了心性论的架构、未发已发说、涵养先于省察的进路,标志朱子心性与工夫思想的基本确立。对于“中和新说”确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王懋竑认为:“按《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皆在已丑之春,盖乍易旧说,犹多有未定之论。……《中庸或问》又谓涵养之功至,则其发也无不中节,又似删却已发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论也。《中和旧说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诸说,则其所见已不同矣。”①王懋竑又提出朱子于1169年的《答林择之》②的三封书信也是“早年未定之论”,他说:“皆辨先察识后涵养之非,而于涵养特重于已发工夫,未免少略……‘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自然发见昭著,不待别求,’是皆早年未定之论,而后来所不取也。”③王懋竑认为朱子40岁时的著名论说均非“定论”。相反牟宗三却十分肯定“中和新说”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他认为“王懋竑所谓‘未定之理论’,无一可通”④。并认为《中和新说》“条贯整齐,朱子学之为静涵静摄系统以及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俱定于此,此乃朱子终身不变者”⑤。他认为朱子涵养工夫在“中和新说”之后就为定论了,他说:“朱子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定论。”⑥陈来则认为朱子“中和新说”代表朱子哲学完整地确立和真正成熟,他认为:“至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⑦又说:“(朱子)40岁的己丑之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基调,从而真正确立了与李侗不同、也与道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的为学方法。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①但是陈来并没有如牟宗三一样认为“中和新说”是定论。朱子在“己丑之悟”的次年(41岁)便作《中庸首章说》②,乾道七年(42岁)又作《胡子知言疑义》③,乾道八年(43岁)又作《仁说》④、《乐记动静说》⑤,对已发未发重新分辨、对心性情做细致的辨析,这都说明朱子对心性论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对此陈来说:“(朱子)此时比己丑之悟时更加明确地用‘未发’‘已发’来规定性情之间的关系。”⑥陈来对朱子40—43岁的状态评价说:“从庚寅到壬辰的思想发展,朱熹明确确认中庸本旨是未发为性,已发为情。”⑦其实,朱子43岁至50岁是朱子思想最高产的阶段,于1172年(43岁)成《论语精义》⑧、《孟子精义》⑨、《资治通鉴纲目》⑩、《西铭解义》⑩,《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成⑫,又于1173年(44岁)成《太极图说解》⑩、《程氏外书》⑩、《伊洛渊源录》⑩,继续修改《仁说》⑩。由此可见,朱子40—44岁是朱子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懋竑认为此时朱子才定下为学之宗旨,王懋竑《朱子年谱》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最早起于1173年朱子44岁。①陈来也说:“自乾道五年己丑之悟到乾道九年癸巳《伊洛渊源录》成,四年之间是朱熹哲学思想建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②朱子1175年(46岁)时与张栻、吴翌、吕祖俭等人对心的工夫展开论辩作《观心说》③,与吕东莱合编《近思录》④,《近思录》的编订意义重大,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四十以后,注《太极图说》,辑《近思录》,渐悔前非。”⑤陈荣捷先生则认为《近思录》“是我国第一本哲学选集。其思想乃朱子本人之哲学轮廓”⑥。同年朱陆会于鹅湖,此时朱子的为学宗旨、思想体系已经基本确立,朱子依自身的为学宗旨和学术规模与陆学展开关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论辩,对此钱穆提出:“鹅湖初会时,朱子之思想体系与其学术规模已大体确立。”⑦陈来则提出:“从40岁到46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⑧由此可见,朱子于40—46岁完成了大部分的思想建构,但从“轮廓”“大体”“基本思想”等表述来看,不能认为46岁时朱子思想建构已完成,因为两年后1177年(48岁)朱子成《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⑨,删定石墪所编《中庸集解》,更名为“中庸辑略”⑩,同年又编成《诗集传》⑪。以《集注》《或问》的编定为标志,朱子完成了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整体建构,确立以《大学》作为学术规模,并贯通《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理论体系,也正式标志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对此牟宗三认为“朱子在‘中和新说’和《仁说》后以《大学》为规模”①似乎言之过早,因为朱子注重《大学》工夫是在《集注》《或问》之后。陈来认为:“此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种种改变或发展,但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稳定地确立起来了。”②所以,由上文分析可知朱子48岁《集注》编订后标志其思想体系正式确立。
三 第三阶段:中晚年思想(49—59岁)
《集注》的形成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但很多问题依然继续展开。《集注》编订后,朱子对《集注》中的许多问题依然在讨论和修改,可以说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贯穿自己的一生。如《语类》中载:“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尽。旧来说作意或未诚,则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说从诚意去。”③这说明朱子改《大学章句》“正心”章至少是在《集注》修订三年以后了。朱子53岁时去信任伯起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后便寄去。”④57岁时,朱子去信程正思说:“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说之不明,方略改定,正与来喻合。”⑤同年,朱子又去信胡季随说:“恭叔所论,似是见熹旧说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处有未尽耳。当时旧说诚为有病,后来多已改定矣。”⑥同年,朱子再去信詹帅书说:“《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论语》《孟子》二书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则鄙拙幸无今日之忧久矣。”①1187年,朱子58岁,他去信程正思两封,第一书说:“告子‘生之谓性’,《集注》虽改,细看终未分明。近日再改一过,此处觉得尚未有言语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细看,他时相见,却得面论。……‘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删去旧论,似已简径。但恐于一原处未甚分明,请看详之。”②第二书说:“《孟子》中间又改一过,不记曾录去否,今恐未曾,别寄一本。”③同年,朱子也去信董叔重说:“书中所喻两义,比皆改定。《大学》在德粹处,《孟子》似已写去矣。……今所改者,亦其词有未莹或重复处耳,大意只是如此也。”④朱子还去信周叔谨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⑤59岁时,朱子去信黄直卿说:“《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仔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⑥可见,朱子在《集注》修订后的十多年间还在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分别进行大量的商榷修改,朱子在这一时期与黄商伯、蔡季通、吕伯恭、黄直卿、吕子约、程正思、王子合、向伯元、陈同甫、刘德华等人的书信达二百一十多篇,其中大量讨论到《集注》的相关问题,花费大量心力。朱子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功不多,50岁时再定《太极通书》①,57岁时成《易学启蒙》②、《孝经刊误》③,58岁成《小学》④。可见在49—59岁,朱子并没有过多的思想著述,其主要精力主要集中在修改《集注》与《或问》,可以说是对其中年时期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修正和完善,对此朱子自己也说:“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⑤
四 第四阶段:晚年思想(60—71岁)
历史上对“朱子晚年”界定不一,由此也造成对朱子晚年思想有不同的结论和判断。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复会于南康,议论之际,必有合者。……盖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归之渐云。”⑥可见,程敏政以朱陆南康之会作为“朱陆晚同”的开始,南康之会时朱子52岁,也就是说在程敏政这里似乎以朱子52岁为晚年。而阳明作《朱子晚定论》,认为朱子晚年觉昨日之非,但未对“朱子晚年”有时间上的说明。后陈建以朱子56岁时《与刘子澄书》⑦为标志,作为朱陆晚年相异的开始⑧,似是以朱子56岁开始为朱子晚年。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明确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⑨。王懋竑校定《朱子年谱》四卷,“以61岁为第四卷开始”①,并说:“晚与门弟子究悉精蕴”②,似是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阶段。近世朱子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刘述先、陈荣捷、陈来等都对“朱子晚年”有过相关讨论,但没有对“朱子晚年”的时间有明确的界定。本书以朱子60岁序定《大学章句》作为其思想进入晚年阶段的标志,60岁朱子与象山也结束了无极太极之辩③,并重新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子对《集注》和《或问》中的许多问题长期思考和修订的结果。所以60岁开始,朱子的生命进入了人生最后的十一年,从思想意义上说朱子人生的最后十一年也是朱子思想最成熟的阶段。
朱子晚年阶段对著述集中在经学的研究上,1192年(63岁)成《孟子要略》④,1196年(67岁)成《仪礼经传通解》⑤,1197年(68岁)成《韩文考异》⑥、《周易参同契考异》⑦,1199年(70岁)又成《楚辞集注》⑧。由此可见,朱子晚年阶段注重对经学思想的阐发,但对《集注》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工夫问题,朱子的讨论没有停止,这在朱子晚年的书信和《语类》中大量呈现。在此期间,朱子与黄干通信多达七十一封,与蔡季通通信多达六十六封,另与刘季章、吴伯丰、刘智夫、巩仲至等各二十余封。《语类》中所载朱子晚年时期与门人、友人讨论问学达五十九人,⑨其中记录了大量朱子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的讨论和说法的修订,对此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年近六十,注《论》《孟》,注《学》《庸》,益加精进。此时议论加意磨勘,于正谊明道中犹防计功谋利之私,而刮之剔之、淘之澄之,务底于平,不敢以己私少戾天理。故年踰七十,病将革矣,犹改《大学》‘诚意’章,绝无私护意。”①可见,朱子对《集注》的讨论和修改持续其一生。
朱子晚年尤重视对《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中的工夫论的讨论和修改。朱子在序定《大学章句》的同年便致信李守约:“《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概已改定,多如所论。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②1190年(61岁)致书张元德说:“《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③又说:“《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④1191年(62岁)致郑子上两封书信,第一封信说:“‘知至意诚’一段来喻得之。旧说有病,近已颇改定矣。其他改处亦多,恨未能录寄也。”⑤第二封信说:“《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⑥同年致书黄直卿:“《大学》向所写者,自谓已是定本,近因与诸人讲论,觉得絮矩一章尚有未细密处……此番出来,更历锻炼,尽觉有长进处。向来未免有疑处,今皆不疑矣。”①1193年(64岁),朱子修订《四书集注》,由曾集刻版于南康(南康本)。②故朱子于1194年(65岁)便去信吴伯丰告诉自己对“南康本”的修改情况,他说:“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义理无穷,尽看尽有恨,此衰年来日无几,不能卒究其业,正有望于诸贤。”③1195年(66岁)朱子又致书吴伯丰说:“《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论也。”④同年亦致书孙敬甫说:“《大学》向来改处无甚紧要,今谩注一本,近看觉得亦多未亲切处,乃知义理亡穷,未易以浅见窥测也。”⑤又于1196年(67岁)致书孙敬甫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大学》亦有改定数处,未暇录去。”⑥1197年(68岁)去信万正淳说:“《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⑦1199年(70岁)朱子又致书刘季章说:“《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⑧可见朱子从60岁到70岁都没有停止对《集注》修改讨论,甚至朱子多次说过改定,他终究无法停止对《集注》的修订,至朱子去世前三日,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①朱子60岁后对心性论和工夫论等诸多观点出现新的说法,体现其对此前思想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是朱子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当代学界,其中不能绕开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讨论。所以,如果要对历史上关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争论有较彻底的解决,就应该回到朱子本身对涵养的论述中去寻找答案。对朱子涵养工夫做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进行脉络化的梳理,首先要对朱子一生的思想做脉络化的考察,大体分出朱子思想的重大转折点和发展阶段,不仅关系到对朱子涵养工夫的正确理解,更关系到对朱子思想观点的最终判定。
第一节 研究意义
涵养工夫是朱子工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子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学界却缺少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脉络化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晚年阶段的工夫思想没有特别的注意,这说明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历史上对朱子涵养工夫认识的论争始于朱陆异同之争,“朱陆晚同”论者希望以朱子晚年的涵养思想为依据,试图“合同朱陆”,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也似乎有此意图,如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朱陆晚年同异”“朱子晚年定论”等相关问题的大量争论,其中朱子涵养工夫也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不仅是朱子工夫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人对朱子思想判定的主要依据。所以,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全面、客观的研究,特别是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脉络化的梳理不仅可以厘清历史上对朱子晚年涵养工夫观点的得失,更直接关系到对朱子哲学的正确理解。
一 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需要深入
朱子重本体,更重工夫,但朱子思想的落实最终是在工夫论上。朱子工夫论的基本架构是继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大工夫进路而来,涵养与致知被称为朱子工夫“翼之两轮”,可见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方法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具体居于什么位置,其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则需要进一步追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涵养与致知是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就确立的两个基本为学进路,又因鹅湖之辩是朱陆二人围绕“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展开的,所以学界认识朱子涵养工夫的地位也多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入手。缺少对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的关注。但是不能否认,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涵养工夫内部之间的关系都是定位涵养工夫在整个工夫论中的地位的重要参照,而这需要做专门的梳理与考察。并且,根据历史上提出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发生了转向,是否真的有变化,如何变化也是需要专门解决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脉络化的梳理才能知晓,同时还要对朱子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做脉络化梳理才能知晓。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思想的研究对以上问题并没有十分重视,对朱子涵养工夫研究的结论多停留于“中和新说”阶段,缺少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进一步探讨的兴趣与意识。以中国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他也认为:“(朱子)40岁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为定论。”①若以牟先生此观点为据,显然没有讨论朱子40岁后涵养工夫的必要,但如此则无法解决学界的诸多争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认识也是不够完整的。因此,要了解朱子涵养工夫的全貌不仅要对“中和新说”之后朱子涵养工夫的思想发展做动态考察以完整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的整体脉络,还要重视朱子40岁之后特别是晚年时期涵养思想的最终结论。也就是说,要全面了解朱子的工夫论,朱子涵养工夫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要对朱子涵养工夫有全面的把握,就应该重视对朱子涵养思想的脉络梳理,特别重视“中和新说”至朱子晚年涵养思想发展的整个脉络,同时也要系统地、动态地考察朱子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涵养工夫与其他工夫的关系,如此才能对朱子涵养工夫有较为完整的、准确的把握。
二 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认识存在误区
学术史上对朱子涵养工夫的争论主要是在朱陆之辩的视域之中进行的,由于朱陆鹅湖之辩的主题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故涵养和致知的关系也成为后人对“朱陆异同”判断的核心内容。对于“朱陆异同”,学界有观点认为象山重“尊德性”而朱子是“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亦有观点认为朱子重“道问学”,轻“尊德性”;较多观点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本,象山以“尊德性”为本;有学者甚至直言:“朱熹是以‘道问学为主’的理学宗旨,陆九渊是以‘尊德性为宗’的心学宗旨。”①无论观点是非对错,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固然是判定“朱陆异同”的重要标准,但是不能把“朱陆异同”的认识局限在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之中,更不能把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异同局限在二者关系的异同,还要回到对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各自工夫本身的异同做进一步的追问。由此,学术史上对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认识就曾出现一种误解,即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没有什么区别,涵养工夫本身不是“朱陆异同”的分歧。这就容易给“朱陆异同”的判断制造一个认识的误区:如果朱子重涵养,则可与象山归同;如果朱子重穷理,则与象山为异。如此,虽然“朱陆异同”的争论延续至今,但争论的焦点更多地还是集中在朱陆之辩的学术事实以及二者“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对比上,最后忽略了对二者涵养工夫异同的注意。这种认识的误区最后直接体现为后世在“朱陆异同”的论争中出现以涵养工夫弥合朱陆的观点,其中以陆王一系提出的“朱陆晚同说”最为典型。“朱陆晚同说”认为朱子在晚年改变了之前的立场,认为“尊德性”重于“道问学”,故折从象山。陆王一系以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判定“朱陆晚同”,与持“朱陆晚异”观点的朱子一系的学者相对峙,持续了很长的论争,甚至最终陷入朱陆、朱王的门派之见中,最终也并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本身有一个客观的、系统的结论,反而加深了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误解。
三 对朱子涵养工夫脉络的判断存在争论
学术史上朱子对涵养工夫脉络的判断出现争论缘于“朱陆异同”之争,陆王一系学者通过对朱子涵养工夫做部分动态的考察,做出了“朱陆晚同”的判定,试图以此来合同朱陆,由此引发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明代程敏政是最早明确提出“朱陆晚同说”的学者,他认为朱子晚年以“尊德性”为重,并认识到自己“道问学”的支离之病。他说:“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见于书者可考也。……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语,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见于义跋;又屡有见于支离之弊,而盛称其为己之功。”①后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虽然阳明并未交代其作《朱子晚年定论》是为了证明“朱陆晚同”的立场,但其在序中说:“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②而《朱子晚年定论》摘录朱子的三十四封书信大多是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内容③,这在当时“朱陆晚年异同”论争的背景下很自然地被列入“朱陆晚同说”的立场,被认为是对程敏政的接续。对此,同时代的学者陈建便说:“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子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卷正相相唱和矣。”①由于阳明及王门后学的学术影响力,《朱子晚年定论》对后人认识朱子涵养工夫以及朱陆异同等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朱子晚年定论》并没有对朱子“晚年”做时间上的说明,对其所引用的书信也没有进行考证和说明,并且对朱子书信的引用还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②,阳明此做法随即引发了罗整庵、陈建等朱子学者的批判,陈建便说:“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③其认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狂误后学之深”④。与陆王学者相对,陈建提出“朱陆早同晚异说”。陈建说:“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殁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⑤他认为:“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⑥可见,陈建认为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是不同的。陈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引起了王门的反对,此后关于朱陆涵养问题的争论则演变为朱王门见论争,二者偏执一方。《四库提要》就指出:“朱陆两派,在宋已分,洎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申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所好。”①但是,朱子晚年涵养工夫本身的真面目却在争论的焦点之外,最终也没有呈现关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真实面貌。
至清代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亦是王学立场,其作《朱子晚年全论》就是为了支持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李绂认为阳明所引朱子书信太少,所以引用了朱子三百多条的书信来证明朱子晚年涵养重于“道问学”,与象山为同。他说:“今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共为一编。”②从内容上看其实是《朱子晚年定论》的扩充版,核心内容仍是朱子涵养工夫,并最终将朱子晚年涵养思想归同于象山。他说:“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则符节相合。”③又说:“陆子主孟子‘先立乎大,求其放心之旨’,则未发之时无不涵养矣。涵养于未发之前,盖延平教朱子之法,而朱子后来弃而不用,晚年始复追寻,有‘孤负此老’之悔。”④又说:“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朱子晚年定论》,陆子既不及闻其说。”⑤但是李绂之说并非完全属实,其所引朱子书信并不是皆在朱子51岁以后,其引朱子《答潘叔度》五书中,书一、书二是在1173年,书三、书四在1174年,书五在1186年,分别为朱子44岁、45岁、57岁,并非都在51岁后。①也并没有真正做到“晚年论学之书,则片纸不遗”②。为了反驳王阳明与李绂,朱子学者王懋竑为此重新校定《朱子年谱》四卷,并作《年谱考异》,“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说”③。然而王懋竑虽然将朱陆之辩的过程考证得十分详细,但并没有正面回应阳明和李绂对朱子晚年涵养思想的判定问题。中华民国学者钱穆先生、现代学者如陈荣捷先生、陈来先生等亦有大量讨论朱陆晚年异同以及《朱子晚年定论》的评判问题,钱穆说:“淳熙十五年与象山争《太极图说》,书问往返,传播远近,而后两人异同之裂痕,遂暴露无遗。其时朱子年已五十九,上距鹅湖初会,先后已历十有四年。此下又四年而象山卒世,又八年而朱子亦没。在此一段时间之内,朱子思想体系进而益密,其学问规模亦廓而益大,然犹是与二陆鹅湖初会时之规辙,而日臻于平实圆通,非有如阳明所谓‘晚年定论’之说也。”④陈荣捷后来总结前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主要有四点:“一为其误以中年之书为晚年所缮;二为其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三为其断章取义,只取其厌烦就约之语与己见符合者;四为其误解‘定本’,且改为‘旧本’。”⑤陈来说:“王阳明之《晚年定论》不顾材料考证,徒据臆想(要其意亦不在考证也),以‘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其实《大学》《中庸》的章句或问皆成于朱熹60岁。而《晚年定论》收书三十二通,其中答何叔京等十一通皆在50岁以前。”①以上朱子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回答了朱陆晚同的立场,却几乎没有从朱子涵养工夫本身的脉络发展上回应历史上对朱子晚年涵养工夫的判定,目前学界对朱子的研究也没有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从确立至晚年的脉络发展状况,所以至今也无法对朱子涵养思想的早晚变化做出判定,最终解决以往的争论。为了解决如上问题,必须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脉络发展做完整的研究。
四 对朱子涵养工夫优劣的判定有待商榷
学术史上对朱子思想的研究至中华民国时期出现一个较大的转向,即对朱子的研究重点从工夫论走向心性论,乃至宇宙观,并最终由此对朱子思想做出优劣的判定。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华港台新儒家多持“尊陆贬朱”的立场,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朱子的涵养工夫劣于象山的涵养工夫,最终延伸到思想系统的优劣。牟宗三说:“心之仁不待仁外之敬以求之也,仁体即敬也。此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创生直贯义,非心、仁、敬三者之关联义也。由此关联义而见其为静涵静摄系统,而非创生直贯之纵贯系统也。”②牟宗三认为朱子与象山之区别在于“横贯”与“纵贯”系统的本质不同,朱子属于“静涵静摄系统”,朱子的涵养工夫是好习惯的养成,非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他说:“若如朱子所论,只于空头的察识外,知尚有未发时,故复补之以空头的涵养,此虽亦可得力,然所养成者只是不自觉的好习惯,以此为本只是外部的空头涵养工夫之为本,非内部的性体本心之实体自身之为本也。”③如此,牟宗三最终将朱子的涵养工夫判定为外在的道德实践的养成,也就是说是被约束和训练而成的德行,而非心内自觉的道德实践,他说:“然此尊德性显然是经验地、外在地。推之,其一切敬的工夫亦都是经验的、外在的。以朱子持身之谨,克制之严,自是尊德性,然是经验地尊、外在地尊,故乏自然充沛之象。”①最终,对朱子的涵养工夫做了经验的、外在的判定。
基于这样的理解,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工夫属于小学工夫,不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而是通过习惯和练习完成的,他说:“朱子以小学教育即为‘做涵养底工夫’,此即为空头的涵养。此是混教育程序与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工夫而为一,而不知其有别也。……即‘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亦仍是不自觉的自然生长,还仍不是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事。”②又说:“其所意谓之涵养只是一种庄敬涵养所成之好习惯,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养习,只是类比于小学之教育程序,而于本体则不能有所决定,此其所以为空头也。”③最终以“空头涵养”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出价值判断。牟宗三基于这样的判定,他认为朱子的涵养并非承于孟子正统,最终对朱子做了“别子为宗”的判定,他说:“是以朱子如此讲空头的涵养以遮‘先识端倪’之本体论的体证,实是混习惯与自觉为一。此皆非孔子讲仁、曾子讲守约战兢、孟子讲本心、《大学》讲诚意、《中庸》讲慎独、致中和之本意。……朱子如此讲涵养显然不够。”④以至于最终,牟宗三对朱子的整个道德体系都做出了“歧出”的判定,他说:“其本体论的体证(体悟)所体证体悟之太极却只成致知格物之观解的,此非延平之静坐以验未发气象之路也,亦非明道‘须先识仁’、五峰‘先识仁体之体’之本体论的体证也,此其所以为歧出也,此其所以终于为他律道德之本质系统,而非自律道德之方向系统,所以终于为静涵静摄系统,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而非本体宇宙论的、即活动即存有的实体之创生直贯义之纵贯系统也。”①综上分析可知,牟宗三判定朱子道德系统为“他律道德”“歧出”“别子为宗”等,这都与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判定是直接相关的。
牟宗三对朱子涵养乃至整个道德系统的判定在学界有很大影响,也影响到后世学者对朱子涵养思想甚至思想系统的判定,现今许多中国港台一系学者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定仍从牟宗三先生之说②,大陆学者亦有此种说法。可以说以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判定是继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定论”,但是此种观点是牟先生自己的创说,是否合乎朱子涵养工夫的本义,实在是有必要做进一步商榷,学界至今对牟宗三判朱子涵养工夫为“他律”之说的也少有回应。要解决以上问题,都需要从朱子涵养工夫本身入手,并对朱子涵养工夫与心性论的关系、涵养工夫与气禀的关系、涵养在其他工夫中的地位等做客观的、全面的梳理才能得知。
第二节 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与不足
总结目前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重视程度和研究程度都远远不够,虽然有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陈来等著名朱子学者在论著中做过专门的讨论,但总体上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论文期刊数量甚至不过百数,这显然与朱子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符,更与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不符。
一 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研究
(一)集中在“中和新说”阶段
学界对涵养工夫脉络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朱子“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时期,对朱子涵养工夫确立后的脉络的发展,特别是对朱子晚年阶段涵养工夫的研究十分缺乏。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下)第三章“中和新说下之浸润与议论”整章探讨朱子“中和新说”后的涵养工夫,他提出朱子“中和新说”涵养工夫就是定论,他说:“新说关于浸润与议论中提出关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之定论。”①其后所附《朱子语类》中的论证材料从朱子41岁开始②,但牟宗三对其所引材料没有进行时间上早晚的区别,说明其对朱子涵养工夫的脉络发展没有特别关注。钱穆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注意到朱子晚年言敬的变化,他说:“朱子于北宋理学诸儒所言心地修养工夫,其纠弹尤多于阐发处。其为儒释分疆划界,使理学一归于儒学之正统,朱子在此方面之贡献,至为硕大。即二程所言,朱子亦复时有匡正。如言敬,朱子则言不可专靠一边。而朱子晚年,则颇似有另标新说,取以代程门言敬之地位者。此层在朱子并未明白直说,要之似不可谓无此倾向。”③可见,钱穆认为朱子晚年言敬与二程有区别,但他的讨论停留于此,并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讨论。唐君毅的朱子学研究花费大量笔墨探讨朱子的涵养工夫,其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附《原德性工夫:朱陆异同探源》上、中、下三编对朱陆涵养工夫的异同做了专题研究④,但唐先生也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有特别的注意。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也花费大量笔墨讨论朱子的涵养工夫①,但也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脉络有专门的注意。
亦有学者注意到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变化,比如曾亦在《宋明理学》中就提出朱子在“中和新说”中认为“未发时未必为中,已发时未必为和,故欲使未发之中,即在未发时加一段功夫,即涵养工夫”②。他在这里加一个注:“朱子此时尚仅强调未发时一段涵养工夫,以为如此则自能使已发之和,后来方觉得已发时之省察工夫亦不可缺。主敬与致知、涵养与省察须互相发,方能无病。”③这说明其发现朱子涵养工夫是有变化的,但却未能对“后来”做时间上的追问与进一步的分析说明。另有陈林在《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一文中提出朱子晚年对已发未发有重新认识,他说:“朱子晚年试图打通涵养主敬与格物穷理两工夫,强调涵养主敬与格物穷理相互渗透、相互发明,在晚年的朱子看来,未发时固然要做存养工夫,已发时亦要做存养工夫,已发时固然要做省察工夫,未发时亦要做省察工夫,要做到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④此观点之是非暂且不论,但此篇论文却是少有的明确以朱子晚年思想作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体现了对朱子涵养工夫在晚年的发展的注意。
(二)对晚年阶段的研究不足
朱子晚年阶段是朱子人生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不加以关注和研究,亦不可能完整了解朱子思想。朱子晚年又是朱子人生阶段的最后时期,可以说,朱子晚年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和判定是朱子思想最后的定论。朱子晚年对某些观点和问题的阐述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反而恰恰代表了朱子一生当中最关切的问题,也是朱子历经一生思考的问题。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来看,哲学家后期的思想往往会呈现更加严密化的特点,注意力往往不再集中于建构新的思想体系,而更加注重对自身思想体系的修建和反思,这亦是朱子思想不断深化的体现。朱子在晚年时期形成的观点其实是朱子思想中最成熟、最可信的阶段,是朱子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但目前学界对朱子晚年阶段的研究却十分不足,对朱子晚年阶段相关思想都缺乏专题研究,没有相关专著,也没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虽有研究朱子学的大家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陈荣捷、陈来等在论著中对“朱子晚年”的相关思想做部分讨论,以朱子晚年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只搜索到约四十四篇,其中直接关系到朱子晚年阶段研究的不到十篇。以上对朱子晚年的研究皆未涉及涵养工夫这一主题,对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只涉及边缘,可以说学界对朱子晚年阶段涵养工夫的专门研究严重不足,缺乏对朱子晚年阶段的涵养工夫思想的代表性观点,这也成为完整认识朱子思想的困难所在。另一方面,由于前人对“朱子晚年”的时间界定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导致现今学界对“朱子晚年”的认识比较模糊,对朱子晚年阶段的研究也十分不严谨,这也是对朱子晚年阶段涵养工夫做专门研究的困难所在。
总结以“朱子晚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大多对“朱子晚年”未做时间上的明确说明,对引用的材料没有进行考证或说明,自然认定为“朱子晚年”。如在《朱陆晚年之异初探》①中所引“朱子晚年”材料是《语类》中“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②一段,由于《语类》中没有注明由谁所录,但笔者也未对其做时间上的证明。其引《朱子语录》中“江西便有这个议论”一段,由甘节录,时间为朱子64岁后①,作者也未进行说明;另引《语类》中“陆子静之学”一段,由贺孙所录,时间为朱子62岁之后②,作者亦未进行说明。可见,作者虽以“朱陆晚年”为研究主题,却并没有对朱子晚年、陆九渊晚年的时间做清晰的界定或者明确的说明。又如在《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③一文中,作者以“朱子晚年”为主题,但在文中没有任何对“朱子晚年”的时间上的说明,更未对所引材料进行考证,对笔者所说的“朱子晚年”无法知晓。所以,对于“朱子晚年”的研究需要以更为严谨的为学方法对朱子人生阶段和思想阶段做一个相对合理的划分,并对引用的相关文献做时间上的辨析和说明,这也是对朱子涵养工夫做脉络化研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及地位研究
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系统中的地位应当是研究朱子涵养工夫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地位的认识主要围绕早期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以及朱陆之辩中涵养与致知的关系的考察。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朱陆之辩的主题,故更偏重对涵养与致知关系的考察,因为持敬是涵养的主要工夫,所以对持敬与穷理的关系,学界研究已经比较透彻,结论比较清楚,存在争议较少,故研究成果本书不再列举。但对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学界的争论比较大。除此之外,由于学界对朱子涵养工夫关注点都在持敬上,对其他的涵养工夫以及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较少,存疑较多。本书总结了学界对朱子诚意与致知、持敬与克己以及持敬与立志三个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一)诚意与致知的关系
1.朱子重致知轻诚意
以牟宗三为代表,他提出朱子诚意是外在的诚、他律的诚,这与他认为朱子的涵养是好习惯的养成而非自觉的道德实践的判断是一脉相承的。牟宗三认为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是“以知言诚”,认为这是朱子诚意工夫的局限,他说:“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粘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之,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①可见,牟宗三认为朱子的致知吞没诚意,朱子偏重致知一方。他又说:“但以此‘真知’说诚意,反过来亦可以说诚意只是知之诚。是则‘真知’与‘诚意’只是一事之二名,意之诚为知所限,而与知为同一。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②由此,牟宗三认为朱子的诚意只是知的落实,而不是行的落实。
牟宗三又进一步说:“是即不得不承认‘意之诚’与‘知之真’为两回事。即是意之诚不与知之真为同一,朱子亦可让意之诚有独立之意义,然而知之机能与行之机能,在泛认知主义之格物论中,只是外在地相关联、他律地相关联,而行动之源并未开发出,却是以知之源来决定行动者,故行动既是他律,亦是勉强,而道德行动力即减弱,此非孟子说‘沛然莫之能于能御’之义也。”③由此,牟先生对朱子做出了“知行不一”的判断,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是“道德无力”。这就是为何牟宗三批评朱子的涵养是“空头涵养”,察识也是“空头察识”的原因,他认为二者都不是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他说:“涵养既空头,则察识亦成空头的。其着力而得力处只在‘心静理明’。涵养的心静故理明。……或在格物穷理处能逐步渗透或静摄那存有之理。此即成全部向外转……此种察识只能决定(静摄地决定)客观的存有之理,而不能决定吾人内部之本心性体。其涵养所决定的,是心气质清明,并无一种超越之体证。其察识所决定的,是看情变之发是否是清明心气之表现,亦非是看本心性体之是否显现。”①
2.朱子重诚意
钱穆与牟宗三不同,钱穆在《朱子新学案》第2册中又专门讨论了“朱子论涵养与省察”②,钱穆认为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朱子工夫论的严密性,他说:“朱子自所主张欠了分数为自欺之根之说,虽非《大学》文本之意,而节去之终为可惜,乃移置于此。……然朱子之说,终始本末一以贯之,兼顾并到,互发互足,则遥为细密而圆满,可遵而无病。有志之士所当明辨审择也。”③钱穆认识到朱子对诚意思想的重视,也对朱子晚年修改诚意的工作做了肯定,他说:“朱子易箦前三日改此‘一于善’三字为‘必自慊’三字,乃与下文注语言‘诚意者自修之首’一句义指相足,工夫始无渗漏。此其用意,可谓精到之至。……是岂单标孤义,杜塞旁门,所谓易简工夫之所能相比拟乎?”④显然,钱穆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工夫,甚至认为朱子的诚意工夫优于象山之易简工夫。
陈来提出朱子晚年仍持“致知在诚意之先”的立场,并且陈来提出这是朱子晚年与象山的区别,他说:“朱熹晚年,陆九渊死后,陆氏门人包显道率人至闽来学,朱熹一见面就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如某便谓须当先知得方始行得。’这里朱熹认为陆氏本意未尝不教人作圣贤,但不读书穷理,无法了解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这样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①可见陈来十分肯定朱子的“诚意”思想,并认为这是朱子优于象山的地方,他说:“朱熹后来意识到,关于气质对人的意识的影响,由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不能自发地达到道德完善(意不能在自诚),以及必须通过长久的认识和磨炼才能去除气质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些方面才是陆学失误真正重要的问题。”②陈来进一步提出,象山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而朱子在认识到气禀对人的影响后更强调做工夫的重要性,这是朱子思想的进步之处。
针对牟宗三对朱子的诚意是“知而不行”的判断,方旭东认为西方哲学在处理“知而不行”问题时,或强调认知,或强调意愿/意志,或归结于非理性自我,而在程朱(尤其是朱熹)这里,这些思考以一种综合的面貌呈现,他认为朱子“知而不行”的“知”只是一种“浅知”,不是“真知”,“真知”之“真”是从“知”的效果上讲的,强调“真切不虚”。这种“真知”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亲身实践的亲知,求知或致知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道”或“见理”的道德践履。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③方旭东显然注意到朱子致知与诚意的关系,注意到朱子的诚意工夫是要贯通知行。
(二)持敬与克己复礼的关系
“克己复礼”来自《论语·颜渊》中的一段,是孔子训示颜回如何为仁的方法,颜回在孔门中地位很高,克己复礼思想得到后世学者推崇。朱子和象山皆言克己的重要,朱子在《仁说》中就提出了克己工夫,象山言“义利之辨”也重克己工夫。历史上亦有持“朱陆晚同”观点的学者以克己工夫合同朱陆,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然朱子晚年,乃有见于学者支离之弊……而陆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之语,见于奠东莱之文。……或乃谓朱陆终身不能相一,岂惟不知象山又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诚。”①钱穆则认为朱陆二人对克己工夫的态度不同,其以《语类》中朱子与陆子寿论“克己复礼”②指出:“朱子主张教人克己复礼,谓众人皆有此病,须克之乃可进。二陆兄弟主张心即理,不喜言克己,故复斋以此归朱子,而朱子以此答之。但尚未辨到克己复礼工夫是一是二。”③钱穆又说:“朱子晚年好提克己工夫,然恐不仅为象山一派所不喜,即一般学者,殆亦多抱颜子地位何待克己之疑。”④可见,钱穆认朱子晚年更重克己,而陆学则不喜克己,这是朱陆言克己的分歧。
钱穆还注意到朱子言克己与敬的关系的变化,他说:“朱子提出《论语》孔子告颜渊以克己,以为求仁之要,一言而举,此意当在其辨已发未发而提出程门敬字之后。”⑤钱穆认为朱子提出克己在提出主敬之后,克己工夫的提出改变了朱子本来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两大工夫架构,他说:“于伊川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项外,特增入克己一项,几于如鼎足有三。”⑥钱穆还提出朱子言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出现了三变,他说:“伊川以《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此注乃以《论语》孔子告颜渊问仁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显已把孔门心法转移了地位。伊川又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先亦引其说,稍后则谓敬之外亦须兼用克己工夫,更后乃谓克己工夫尚在主敬工夫之上。关于此,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①钱穆后来又在《朱子新学案》中详细分析了朱子言克己的变化,他认为朱子46岁时对于克己工夫的认识是:“克己、复礼分作两项说,又谓克去己私了,正好着精细工夫,则克己工夫只是初步。……殆此时朱子仍遵程说也。”②钱穆提出:“朱子五十以后……以克己与敬与致知并列为三,而必先言伊川所以只言涵养不言克己之意,然后始言涵养克己亦可各作一事。”③他说:“朱子年六十以后,乃始于克己工夫表出其十分重视之意。”④又说:“及其年过六十,乃始明白以克己工夫放在持敬工夫之上。”⑤可见,钱穆认为朱子越来越重视克己,认为朱子60岁后对克己工夫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持敬,最后钱穆提出朱子改变了以涵养和致知为两个工夫架构,并以克己为第一等工夫,他说:“伊川所谓敬义夹持,涵养致知须分途并进,其实也还落在第二等。须如朱子所发挥颜子克己工夫,乃始有当于圣门为学之第一等工夫。”⑥可见,钱穆认为朱子对克己的重视已超过了持敬,由于学界对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关注得不多,钱穆的观点没有引起很多讨论,但朱子晚年后的工夫架构是否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需要对朱子论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做脉络化的梳理才可知晓。
(三)持敬与立志的关系
对于朱子立志工夫的研究,学界关注得十分少,但钱穆对朱子立志工夫有较早的注意,他认为:“朱子特拈立志一项,已在晚年。朱子立志的工夫是为了补居敬工夫之缺”①可见,钱穆认为朱子晚年时提出立志工夫是为了补充持敬工夫的不足。钱穆认为朱子晚年提出立志工夫是其晚年工夫思想更加通达的体现,他说:“此谓闲时不吃紧理会,不仅陆学轻视学问有此弊,即专务居敬,不兼穷理,亦必有此病。而朱子尽把来归在不曾立志上,此见朱子晚年思想之力趋简易而又更达会通处。”②可见,钱穆认为象山工夫之缺在于专务居敬,没有兼顾穷理,而朱子晚年把成德失败归于立志工夫,这是朱子晚年思想简易又通达的表现。钱穆又说:“徒尚立志,不务向学,诚是偏颇。然徒知庄敬持养,而不重立志,亦是有病。故朱子教人相资为益。后人徒言程朱言居敬,此皆未细读朱子书,故不知朱子晚年思想之不断有改进处。”③钱穆认为朱子晚年重立志,是二程言敬与象山言立志的结合,是晚年工夫思想严密的体现,而这与朱子晚年的心性论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他说:“朱子晚年又论志与意之分别,提出意属私,故须诚意,志则能立便得,更无有立伪志者。理学家中,惟朱子最善言心……惟朱子言心学工夫,最于理学家中为细密而周到,细看上列诸章自见。”④由此可见,钱穆从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的重视看到朱子晚年心性论的完善,从而认为朱子言心学工夫最为严密,对朱子晚年言立志工夫做了肯定。
在此基础上,钱穆又对朱陆二人言立志工夫做了对比,钱穆认为虽然朱子言立志有承袭象山的部分,但朱陆二人的立志工夫有本质的不同,他说:“象山教人立志,朱子晚年亦教人立志,此见朱子肯兼取陆学之长。但陆学只言立志,不言学,故朱子特举五峰说以救其弊。此见朱子之博采,亦见朱子立言,必斟酌而达于尽善之境。”⑤钱穆认为朱子晚年言立志是朱子取陆学之长的体现,但陆学言立志有弊即在于只言立志,不言“道问学”,所以朱子取五峰之说,将立志与问学相互补充,这是朱子晚年工夫思想完善的体现。但是钱穆强调朱子晚年虽重立志但不是转从陆学,他说:“是朱子晚年虽履告学者以立志,终不得谓是转从陆学。”①钱穆对朱陆二人言立志工夫做了区别,他说:“象山教人立志,似只重当下行处。朱子谓人不立志则不肯闲时吃紧理会,则偏重知一边说。此两家同言立志而意趣有别也。”②可以看出,钱穆认为陆学言立志偏向行,朱子言立志偏向知,这是二者言立志的区别,是否如此也要对朱子立志工夫做细致的梳理才可知晓。唐君毅亦注意到朱陆二人言立志的不同,他认为朱子对立志的重视不如象山,他说:“朱子晚年又尝谓:‘从前朋友来此,某将谓不远千里而来,须知个趣向,只是随分为他说个为学大概。看来都不得力。今日思之,学者须以立志为本。’然只以趣向为志,似不够分量。观朱子于五峰所谓‘志立乎事物之表’之一义,亦实未能如象山之重视。”③唐君毅认为朱子虽然重视立志,但只是立乎事物之表,但重视的程度不如象山。可见钱穆、唐君毅均注意到朱子晚年言立志工夫,但二人对朱子言立志工夫都有不同的评价,至于晚年朱子对立志工夫重视的程度如何,其与持敬的关系如何,二人的判断是否中肯,需要对涵养与立志关系的脉络进行梳理后才可知。
三朱陆涵养工夫异同研究
学界对朱陆异同的判断多是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去讨论,所以学界在对朱陆涵养异同研究中不免要对二者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进行讨论。牟宗三认为朱陆的差异是二者思想系统的不同,他说:“依吾人现在观之,‘陆氏之学与朱子合下不同’此诚然也。但此不同根本是孟子学与《中和新说》之不同。”①牟宗三认为朱陆不同是朱子的“中和新说”与孟子“求放心”思想的根本不同,朱子“中和新说”确立涵养思想,牟宗三意指朱子涵养思想与孟子“求放心”不相契,而象山从孟子,这是朱陆二人涵养不同的原因。牟宗三又从朱子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判定朱子涵养工夫是经验的、外在的道德实践,而象山则是自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他说:“尊德性琐碎委散于道问学之中,全幅心力集中于道问学,而尊德性则徒见其随道问学而委散,而不见其直承天心仁体之提挈,此所以象山观之,并未尊得起。朱子亦觉此病,故认从象山游者,于践履上皆有气象可观,而自己之门人,则虽读了许多典策,却无甚挺拔处。……凡此种道问学中之尊德性,皆是经验的、外在的,惟赖戒慎于风习名教而不敢逾越以维持其尊德性;此是消极地尊,并非积极地尊。盖其主力在知识典策,故其所成亦在此。……是则朱子之途径实是道问学之途径(为学日益),于学术文化自有大贡献,而于成圣成贤之学问(为道日损)则不甚相应也。”②在此,牟宗三明确认为朱子重“道问学”而轻“尊德性”,认为朱子的“尊德性”工夫受到“道问学”的限制而成为“道问学”中的“尊德性”,是经验的、外在的、他律的“尊德性”,不是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所以朱子在“道问学”工夫上有很大贡献,但相比“尊德性”,真正实践工夫就差很多了。在此基础上,牟宗三对朱陆二人的工夫进路做了判定,他说:“朱子与五峰、象山之异,根本是顺取之路与逆觉体证之路之异,并不是笼统地‘自下面做上去’与‘自上面做下来’这单纯的两来往之异,亦不是从散到一与从一到散之异。”③基于牟宗三对朱子“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认识,牟宗三认为朱子的“下学而上达”是“逆觉体证”,象山是“顺取”,象山的成德路径优于朱子。
唐君毅认为朱陆的不同首先在于工夫的不同,而工夫的不同首要是涵养工夫的不同,而二者涵养工夫不同的原因在于二者对心与理关系认识的不同。唐君毅说:“吾人谓朱陆异同之第一义在二贤之工夫论,唯在此工夫论之有此异同,而朱陆乃有互相称许之言,亦不免于相非。至在朱子晚年之言论,如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辑,其非议陆子之言尤多。”①他认为朱子晚年多非陆学,而朱陆不同的第一义在于工夫的不同,这种工夫的不同又首先在于涵养的不同,他说:“其早年鹅湖之会中,于尊德性道问学之间,各有轻重先后之别,不能即说为根本之不同甚明。而朱子与象山在世时讲学终未能相契,其书札往还与告门人之语,或致相斥如异端者,乃在二家之所以言尊德性之工夫之异,随处可证。”②可见,唐君毅认为鹅湖之会时,朱陆二人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各有轻重先后之别,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先、为重,象山以“尊德性”为先、为重,他又认为二者终未能归同的原因在于二者“尊德性”工夫的不同,亦即涵养工夫的不同。唐君毅对朱子的判断是否符合朱子思想本身需要进一步证明,但其指出朱陆二人的不同最终归于“尊德性”工夫上,而这种不同又决定了朱陆二人思想系统的不同,这为朱陆异同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唐君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朱陆异同”争论的根源最后都转向心与性理的问题上,他说:“整庵与阳明之宗主不同,然其以朱陆之异在心与性之问题则一。下此以往,凡主程朱者,皆谓陆王之重心,为不知格物穷理而邻于禅。如陈清澜《学蔀通辨》,论朱陆早同晚异,陆学唯重养神,张武承《王学质疑》,亦疑阳明言非实理也。王学之流,则又皆明主心与理一。……则言朱陆之异同,当在此心与性理之问题上措思,固阳明以降宗朱子与宗陆王者共许之义也。”①
唐君毅还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和朱止泉著“朱子未发涵养辨”一章,并认为二者“皆谓朱子之未尝不先尊德性、务涵养而重践履,而合乎陆子”②。唐君毅反对二人以涵养工夫合同朱陆的观点,他说:“今如缘二贤皆重涵养,谓朱陆本无异同,则又将何以解于朱陆在世时论学所以不相契之故?又何以解于后世之宗朱或宗朱陆者,其学风所以不同之故?以此言会通朱陆,抑亦过于轻易。”③唐君毅认为朱陆涵养工夫的不同归根结底在于二者心与理的关系不同,心性论的不同导致工夫上无法合同。他说:“此其义与象山之言工夫,唯在剥落去人心之病障,以自复其本心,而发明其本心,以满心而发之旨,初无大不同;而在与其宇宙论上或泛论工夫时看心之观点,明有不一致处。”④他又认为阳明契于象山心即理之说,而判定朱子“心理为二”是因为他“已知朱陆之异,不在尊德性与否,而在所以尊德性之工夫与对心理之是一是二之根本见解之异同上”⑤。他提出朱陆异同应该从心性论上找原因,他说:“则言朱陆之异同,当在此心与性理之问题上措思,固阳明以降宗朱子与宗陆王者共许之义也。”⑥从唐先生的观点可知朱陆二人的涵养工夫的异同需要到朱陆二人的心性论上去寻找,同样,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离不开朱子的心性论,朱子涵养工夫变化的原因也要回到心性论上去寻找。
钱穆对朱陆涵养工夫的异同有较多研究,他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提出朱陆二人都有未发涵养这一层工夫,他说:“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①可见当时钱穆认为朱陆都有未发涵养工夫,似以二者涵养为同,钱穆又认为清儒对“朱陆异同”的争论都在文字之间考证求索,故没有看到二人之同。后来,钱穆又提出朱陆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的不同,他说:“象山可谓能开示学者以为学有本之道,而朱子尤必进之以本末精粗之一贯。两人间所以终不能相悦以解。后人以象山之非朱,遂疑朱子为学,只在博览精考。或疑朱子论学之有本,乃与象山交游后晚年之所悟。则试考之淳熙乙未鹅湖相会以前朱子论学之经过,亦可以见其言之无稽矣。”②可见,钱穆认为象山重“尊德性”,而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一贯,二者不能为同。钱穆提出认为朱子只重“道问学”是因为没有看到朱子的“尊德性”工夫早在鹅湖之会前就已确立,并且对“尊德性”的重视持续至晚年。钱穆说:“乃后之尊朱者,又必谓朱子是时尊德性之学已熟,‘今觉得未是’一语不可泥。在此以前,朱子亦极注意尊德性工夫,常作反省,常自以为未是。及其晚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何尝不可自觉未是。且朱子所自以为未是这,似指其教人方面,重说了道问学,轻说了尊德性。两边相比,不免于若此。其谓未是,却不是要专重尊德性,不重道问学。”③钱穆以颜回赞美孔子的话来形容朱子晚年的工夫境界,这本是朱子称赞颜回的话,朱子说:“颜子穷格克复,既竭吾才,日新不息,于是实见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④他认为朱陆皆重“涵养”,强调朱子对涵养工夫的重视从鹅湖之会前直至晚年,只是朱子在教人时重说了“道问学”,轻说了“尊德性”,才使世人造成了误解。
陈来明确反对以涵养合同朱陆,他认为朱子在己丑后,“确认了心有未发之时和已发之际,强调已发时须省察,未发时更当涵养,以未发涵养为本,敬字贯通动静,这些都说明朱学中本来包含着重视涵养的一面。己丑后至壬辰《仁说》之辩论,朱熹心性哲学的体系已全面形成并日趋成熟,他的心为知觉、心具众理、人心道心说以及主敬穷理、涵养进学的方法的确立使他与稍后的陆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所以,在鹅湖之前朱熹根本不是‘未会而同’,相反,他自己早已走上了一条与陆学完全相反的为学道路,从鹅湖前后开始,他对陆九渊的一切公开反驳,都是他自己的学问主张完全合乎逻辑的一个结果”①。在此,陈来认为朱子在《仁说》后涵养的基本方法和立场与陆学的涵养工夫从根本上出现了区别,所以朱陆涵养工夫是不能为同的。陈来在对朱陆之辩的书信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朱子对象山的攻击是因为发现了二者涵养工夫的不同,他说:“淳煕乙巳后,朱熹不再称陆学持守收敛之功,更多地开始强调其狂妄粗率之病而表示忧虑。”②可见,陈来认为朱子56岁后不再肯定陆学的涵养工夫,反而对其狂妄粗率之病表示忧虑,其转变的原因在于意识到自身与象山涵养工夫的不同。他说:“朱熹不但重视致知进学,也重视涵养本原,即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但朱熹之尊德性与陆学不同,不是专求发明本心,而是取伊川‘涵养须用敬’,强调主敬功夫。在外则庄整齐肃,于视听言动、容貌词气上下工夫;在内侧则主一无适,常切提撕,不令放佚。故从朱熹看,陆门学者专求什么顿悟本心,而把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纳入礼教范围方面却毫无作用,以致‘颠狂粗率尔于日用常行之处不得所安’成为陆门的一个普遍流弊。这一点是朱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注意和考虑过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陆学越来越感到不安,以致最终对陆学转而采取了全面、激烈的批判态度。”①如此可见,陈来认为朱子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并不是偏重“道问学”一方,但他指出朱陆二人“尊德性”的工夫是不同的,象山的涵养是发明本心,朱子则是主敬涵养,以前没有注意到象山涵养工夫的弊端在于专务本心而失去礼法的制约,但在注意到象山涵养工夫没有礼的规范后才对象山采取全面、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此,陈来指出认识到二者涵养工夫的不同是朱子56岁后对陆学激烈批判的原因所在,陈来认为这种不同是朱陆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即否定了“朱陆晚同说”。陈来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其指出了朱陆涵养方法的不同,朱子是主敬涵养,也指出朱子注重礼法的制约,朱子注重礼法的制约必定会影响到他对工夫论的诠释,也体现在朱子涵养工夫的变化之中,这都有待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学界已对朱子涵养工夫的部分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已经提出了一些代表性观点,但由于学者们研究主题的不同,导致研究程度不一、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研究不够全面的情况,如对朱子中年时期涵养工夫的确立有较多的研究,对涵养整个脉络的发展则缺少关注;对涵养和致知的关系有较多的研究,对涵养和其他工夫的关系则较少注意;对心性论和涵养工夫都各有研究,但对二者的关联则较少注意。这都说明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空间很大,研究价值很高。再者,由于几位最具代表性的朱子学者对本专题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涉及人物和思想的优劣判定,所以,可以说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许多结论有待进一步追究和检查。本书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研究将以时间为线索,对朱子不同阶段关于涵养的主要观点和在工夫论中的地位进行详细梳理,以对朱子涵养工夫有系统的了解。在对工夫论的研究中,以“工夫不离本体”为思想指引,进一步探寻朱子每一时期工夫思想的变化与心性论的关系,将朱子心性论的发展与工夫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勾勒出朱子思想发展的整体样态。与此同时,以朱子在不同时期与湖湘学、浙学、陆学及程门后学等著名学者的交流与论辩为暗线,一方面对朱子在每一时期涵养工夫的特点做理论和现实上的说明,从而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变化进行立体化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从朱子与其他学派学者的思想碰撞中寻找独属于朱子本身的思想特色和价值。
第三节 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
对朱子思想做阶段划分自古有之,如明代学者陈建将朱子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①,李绂不同意陈建,对朱子做了不同的早、中、晚三阶段的划分。②王懋竑将《朱熹年谱》分为四卷,貌似将朱子思想分为四个阶段,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③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分歧,是因为不同思想家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陈建、李绂围绕“朱陆异同”的主题进行划分,而王懋竑则基于其对朱子生平的考证进行划分。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以朱子年岁为参考,结合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将朱子思想发展做四个阶段划分。
一 第一阶段:早年思想(22—39岁)
朱子的早年思想阶段即学者研究朱子的起始阶段,对此前人有不同的说法和界定,如牟宗三论述朱子思想是从其11岁开始①,钱穆则明确将朱子早年界定为“从游延平前”,也就是24岁前。②陈来作《朱子哲学研究》将朱子“早年”界定于其从学“三君子”至李侗卒,即朱子34岁前。③本书将朱子成年后有了相关论述但尚在探讨阶段的阶段称为“早年思想”,本书将此阶段定为朱子22岁至39岁。
对于朱子哲学思想的开端,学界一般以朱子24岁初见李侗为标志。如牟宗三以朱子24岁初见延平为朱子37岁前思想的第一阶段。④陈来亦说:“朱子早年思想演进,以从学李延平为关键,此在年谱皆已指明。”⑤他提出:“24岁赴任同安途中,拜见了杨时二传弟子李侗。在李侗的引导下,他逐步确立了道学的发展方向。”⑥对于朱子思想的起始,除了朱子的学术交往之外,也可以从其最早的著述窥其端倪。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最早的著述是朱子校订《上蔡先生语录》,他说:“于三十岁(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成《上蔡语录》,此为朱子著述之最早者。”⑦然而初会李侗在30岁之前,显然不能成为探讨朱子思想的开端。除专著外,《文集》所载中尚有更早的论述,陈荣捷认为《文集》“由二十四岁(绍兴二十三年葵酉,1153)至易箦前一日致其门人黄干(1152—1221年),一生著述,除专著外,皆备于此”⑧。陈先生认为《文集》中最早的论述从1153年朱子24岁开始,但是没有具体指出朱子最早论述的内容是什么。后据陈来考证朱子《文集》中最早著述从1151年开始有八篇,如《题谢少卿药园二首》①、《晨起对雨二首》②、《残臈》③等,朱子最早通信开始于1155年,当年朱子有书信八封,如《答戴迈》④、《答林峦》⑤等。《语类》最早由杨子直所录,从乾道六年开始,所以《语类》所载皆为朱子41岁及以后。⑥由此看来,朱子思想的开端可从朱子22岁的诗作开始。
朱子从24岁至34岁从学于李侗,1159年(30岁)校订《上蔡语录》⑦,1163年(34岁)编《论语要义》⑧、《论语训蒙口义》⑨、《延平答问》⑩,1164年(35岁)成《困学恐闻》,至37岁“中和旧说”(丙戌之悟)⑪,朱子自述:“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⑫所以可知以朱子37岁前思想为未定之说是比较明确的。对此,牟宗三说:“然在朱子,三十七岁前犹无‘的实见处’”⑬,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前,对于《中庸》《易传》所洞悟之实体、道体,虽亦有一仿佛之影子,对于《孟子》之本心,甚至《论语》之仁,亦似有一仿佛之影子,然契悟不真,用不上力。”①又说:“朱子在三十七岁以前,虽已确定以《中庸》(首章)、《大学》为入路,对于其内容,则大体只是笼统肤谈。其真切用功是在三十七岁以后。”②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37岁)。”③
37岁至40岁是朱子思想的重要转折期,朱子1167年(38岁)与张栻讨论《中庸》未发已发要旨、先察识后涵养等说④,然而很快朱子又推翻了“丙戌之悟”和“先察识之说”,这点从朱子自述中可以看出;1168年,朱子39岁,成《二程遗书》;1169年,朱子40岁,提出“中和新说”(己丑之悟)⑤,他说:“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⑥可见,朱子自己也说其40岁时改变了此前的论说,明代刘洪谟在《朱子文集大全》序中说:“盖朱子四十以前,如《存斋记》、《答何叔京》二书,专说求心见心,是犹驰心之玄妙,未悟天理时语也。”⑦牟宗三也说:“四十岁以前犹未有此‘的实见处’也。”⑧他认为朱子“新说”后才开始确定其思想的基本架构也是依据朱子的《中和旧说序》做出的判断,他说:“至四十岁因与蔡季通问辨,忽然开朗……遂将此‘天命流行之体’拆散而转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①对此,陈来也说:“朱子思想,成熟于丙戌,确立于己丑。”②可见,学界对朱子这一阶段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对于朱子37—40岁的未定之论,牟宗三将其称为朱子“‘中和旧说’的浸润和议论时期”,是对“中和问题”的参究和发展,他说:“在三十七至四十岁之间,朱子对于此‘天命流行之体’,寂感真几,创生之实体,并无真切而相应之契悟,只是仿佛有一个笼统的影像。”③陈来则说:“朱熹早年中和思想曾经有过两次重要演变(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④以上陈述都说明朱子早年未定之说应该包含37—39岁,所以本书亦以“中和新说”为标志,将朱子22—39岁的思想作为朱子思想的早期阶段,也可以叫朱子早年的“未定之说”。在此期间,朱子著述(大部分是书信)约二百六十一篇。⑤
二 第二阶段:中年思想(40—48岁)
对于朱子中年时期的界定,学界也有若干个观点,比如牟宗三认为朱子37岁时已是中年,他说:“人生三十七已进中年,不可谓少。”⑥但牟宗三所说中年是自然生命意义上的中年,本书以朱子40岁“中和新说”后朱子开始确立自身的思想系统,说明朱子进入中年时期的思想阶段。朱子40岁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⑦、《已发未发说》⑧、《答张钦夫书》“诸说例蒙印可”⑨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的确立,“中和新说”代表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中和新说”后朱子确立了心性论的架构、未发已发说、涵养先于省察的进路,标志朱子心性与工夫思想的基本确立。对于“中和新说”确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王懋竑认为:“按《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皆在已丑之春,盖乍易旧说,犹多有未定之论。……《中庸或问》又谓涵养之功至,则其发也无不中节,又似删却已发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论也。《中和旧说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诸说,则其所见已不同矣。”①王懋竑又提出朱子于1169年的《答林择之》②的三封书信也是“早年未定之论”,他说:“皆辨先察识后涵养之非,而于涵养特重于已发工夫,未免少略……‘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自然发见昭著,不待别求,’是皆早年未定之论,而后来所不取也。”③王懋竑认为朱子40岁时的著名论说均非“定论”。相反牟宗三却十分肯定“中和新说”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他认为“王懋竑所谓‘未定之理论’,无一可通”④。并认为《中和新说》“条贯整齐,朱子学之为静涵静摄系统以及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俱定于此,此乃朱子终身不变者”⑤。他认为朱子涵养工夫在“中和新说”之后就为定论了,他说:“朱子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定论。”⑥陈来则认为朱子“中和新说”代表朱子哲学完整地确立和真正成熟,他认为:“至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⑦又说:“(朱子)40岁的己丑之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基调,从而真正确立了与李侗不同、也与道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的为学方法。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①但是陈来并没有如牟宗三一样认为“中和新说”是定论。朱子在“己丑之悟”的次年(41岁)便作《中庸首章说》②,乾道七年(42岁)又作《胡子知言疑义》③,乾道八年(43岁)又作《仁说》④、《乐记动静说》⑤,对已发未发重新分辨、对心性情做细致的辨析,这都说明朱子对心性论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对此陈来说:“(朱子)此时比己丑之悟时更加明确地用‘未发’‘已发’来规定性情之间的关系。”⑥陈来对朱子40—43岁的状态评价说:“从庚寅到壬辰的思想发展,朱熹明确确认中庸本旨是未发为性,已发为情。”⑦其实,朱子43岁至50岁是朱子思想最高产的阶段,于1172年(43岁)成《论语精义》⑧、《孟子精义》⑨、《资治通鉴纲目》⑩、《西铭解义》⑩,《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成⑫,又于1173年(44岁)成《太极图说解》⑩、《程氏外书》⑩、《伊洛渊源录》⑩,继续修改《仁说》⑩。由此可见,朱子40—44岁是朱子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懋竑认为此时朱子才定下为学之宗旨,王懋竑《朱子年谱》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最早起于1173年朱子44岁。①陈来也说:“自乾道五年己丑之悟到乾道九年癸巳《伊洛渊源录》成,四年之间是朱熹哲学思想建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②朱子1175年(46岁)时与张栻、吴翌、吕祖俭等人对心的工夫展开论辩作《观心说》③,与吕东莱合编《近思录》④,《近思录》的编订意义重大,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四十以后,注《太极图说》,辑《近思录》,渐悔前非。”⑤陈荣捷先生则认为《近思录》“是我国第一本哲学选集。其思想乃朱子本人之哲学轮廓”⑥。同年朱陆会于鹅湖,此时朱子的为学宗旨、思想体系已经基本确立,朱子依自身的为学宗旨和学术规模与陆学展开关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论辩,对此钱穆提出:“鹅湖初会时,朱子之思想体系与其学术规模已大体确立。”⑦陈来则提出:“从40岁到46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⑧由此可见,朱子于40—46岁完成了大部分的思想建构,但从“轮廓”“大体”“基本思想”等表述来看,不能认为46岁时朱子思想建构已完成,因为两年后1177年(48岁)朱子成《四书章句集注》与《四书或问》⑨,删定石墪所编《中庸集解》,更名为“中庸辑略”⑩,同年又编成《诗集传》⑪。以《集注》《或问》的编定为标志,朱子完成了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整体建构,确立以《大学》作为学术规模,并贯通《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理论体系,也正式标志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对此牟宗三认为“朱子在‘中和新说’和《仁说》后以《大学》为规模”①似乎言之过早,因为朱子注重《大学》工夫是在《集注》《或问》之后。陈来认为:“此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种种改变或发展,但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稳定地确立起来了。”②所以,由上文分析可知朱子48岁《集注》编订后标志其思想体系正式确立。
三 第三阶段:中晚年思想(49—59岁)
《集注》的形成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但很多问题依然继续展开。《集注》编订后,朱子对《集注》中的许多问题依然在讨论和修改,可以说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贯穿自己的一生。如《语类》中载:“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尽。旧来说作意或未诚,则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说从诚意去。”③这说明朱子改《大学章句》“正心”章至少是在《集注》修订三年以后了。朱子53岁时去信任伯起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后便寄去。”④57岁时,朱子去信程正思说:“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说之不明,方略改定,正与来喻合。”⑤同年,朱子又去信胡季随说:“恭叔所论,似是见熹旧说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处有未尽耳。当时旧说诚为有病,后来多已改定矣。”⑥同年,朱子再去信詹帅书说:“《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论语》《孟子》二书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则鄙拙幸无今日之忧久矣。”①1187年,朱子58岁,他去信程正思两封,第一书说:“告子‘生之谓性’,《集注》虽改,细看终未分明。近日再改一过,此处觉得尚未有言语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细看,他时相见,却得面论。……‘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删去旧论,似已简径。但恐于一原处未甚分明,请看详之。”②第二书说:“《孟子》中间又改一过,不记曾录去否,今恐未曾,别寄一本。”③同年,朱子也去信董叔重说:“书中所喻两义,比皆改定。《大学》在德粹处,《孟子》似已写去矣。……今所改者,亦其词有未莹或重复处耳,大意只是如此也。”④朱子还去信周叔谨说:“《论语》别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⑤59岁时,朱子去信黄直卿说:“《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仔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⑥可见,朱子在《集注》修订后的十多年间还在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分别进行大量的商榷修改,朱子在这一时期与黄商伯、蔡季通、吕伯恭、黄直卿、吕子约、程正思、王子合、向伯元、陈同甫、刘德华等人的书信达二百一十多篇,其中大量讨论到《集注》的相关问题,花费大量心力。朱子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功不多,50岁时再定《太极通书》①,57岁时成《易学启蒙》②、《孝经刊误》③,58岁成《小学》④。可见在49—59岁,朱子并没有过多的思想著述,其主要精力主要集中在修改《集注》与《或问》,可以说是对其中年时期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修正和完善,对此朱子自己也说:“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⑤
四 第四阶段:晚年思想(60—71岁)
历史上对“朱子晚年”界定不一,由此也造成对朱子晚年思想有不同的结论和判断。如程敏政在《道一编》中说:“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复会于南康,议论之际,必有合者。……盖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归之渐云。”⑥可见,程敏政以朱陆南康之会作为“朱陆晚同”的开始,南康之会时朱子52岁,也就是说在程敏政这里似乎以朱子52岁为晚年。而阳明作《朱子晚定论》,认为朱子晚年觉昨日之非,但未对“朱子晚年”有时间上的说明。后陈建以朱子56岁时《与刘子澄书》⑦为标志,作为朱陆晚年相异的开始⑧,似是以朱子56岁开始为朱子晚年。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明确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⑨。王懋竑校定《朱子年谱》四卷,“以61岁为第四卷开始”①,并说:“晚与门弟子究悉精蕴”②,似是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阶段。近世朱子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刘述先、陈荣捷、陈来等都对“朱子晚年”有过相关讨论,但没有对“朱子晚年”的时间有明确的界定。本书以朱子60岁序定《大学章句》作为其思想进入晚年阶段的标志,60岁朱子与象山也结束了无极太极之辩③,并重新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子对《集注》和《或问》中的许多问题长期思考和修订的结果。所以60岁开始,朱子的生命进入了人生最后的十一年,从思想意义上说朱子人生的最后十一年也是朱子思想最成熟的阶段。
朱子晚年阶段对著述集中在经学的研究上,1192年(63岁)成《孟子要略》④,1196年(67岁)成《仪礼经传通解》⑤,1197年(68岁)成《韩文考异》⑥、《周易参同契考异》⑦,1199年(70岁)又成《楚辞集注》⑧。由此可见,朱子晚年阶段注重对经学思想的阐发,但对《集注》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工夫问题,朱子的讨论没有停止,这在朱子晚年的书信和《语类》中大量呈现。在此期间,朱子与黄干通信多达七十一封,与蔡季通通信多达六十六封,另与刘季章、吴伯丰、刘智夫、巩仲至等各二十余封。《语类》中所载朱子晚年时期与门人、友人讨论问学达五十九人,⑨其中记录了大量朱子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的讨论和说法的修订,对此明代刘洪谟便说:“(朱子)年近六十,注《论》《孟》,注《学》《庸》,益加精进。此时议论加意磨勘,于正谊明道中犹防计功谋利之私,而刮之剔之、淘之澄之,务底于平,不敢以己私少戾天理。故年踰七十,病将革矣,犹改《大学》‘诚意’章,绝无私护意。”①可见,朱子对《集注》的讨论和修改持续其一生。
朱子晚年尤重视对《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中的工夫论的讨论和修改。朱子在序定《大学章句》的同年便致信李守约:“《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概已改定,多如所论。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②1190年(61岁)致书张元德说:“《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③又说:“《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④1191年(62岁)致郑子上两封书信,第一封信说:“‘知至意诚’一段来喻得之。旧说有病,近已颇改定矣。其他改处亦多,恨未能录寄也。”⑤第二封信说:“《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⑥同年致书黄直卿:“《大学》向所写者,自谓已是定本,近因与诸人讲论,觉得絮矩一章尚有未细密处……此番出来,更历锻炼,尽觉有长进处。向来未免有疑处,今皆不疑矣。”①1193年(64岁),朱子修订《四书集注》,由曾集刻版于南康(南康本)。②故朱子于1194年(65岁)便去信吴伯丰告诉自己对“南康本”的修改情况,他说:“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义理无穷,尽看尽有恨,此衰年来日无几,不能卒究其业,正有望于诸贤。”③1195年(66岁)朱子又致书吴伯丰说:“《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论也。”④同年亦致书孙敬甫说:“《大学》向来改处无甚紧要,今谩注一本,近看觉得亦多未亲切处,乃知义理亡穷,未易以浅见窥测也。”⑤又于1196年(67岁)致书孙敬甫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大学》亦有改定数处,未暇录去。”⑥1197年(68岁)去信万正淳说:“《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⑦1199年(70岁)朱子又致书刘季章说:“《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⑧可见朱子从60岁到70岁都没有停止对《集注》修改讨论,甚至朱子多次说过改定,他终究无法停止对《集注》的修订,至朱子去世前三日,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①朱子60岁后对心性论和工夫论等诸多观点出现新的说法,体现其对此前思想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是朱子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附注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①姜国柱:《中国历代思想史》(宋元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①(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道一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②(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40页。
③阳明引朱子《答吕子约》:“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引《答陆子静》:“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引《答周叔谨》:“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像甚适。每劝学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引《答吕伯恭》:“道间与季通讲论,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引《答潘叔恭》:“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引《答潘叔昌》:“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引《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见(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41、141、143、143、145、149、142页。
①(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3页。
②后世学者吴长庚编也说:“程敏政之编《道一编》,取两家言论比较异同,目的只在证其晚同,明其道一。那么,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单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则显然说是援朱入陆,阳朱阴陆,与程敏政有着明显的不同。他通过对书信的选辑,把仅仅体现了朱子心学思想的部分资料,扩大为代表晚年思想的定论,为他自身的心学思想张本。”(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序言》,《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2页。
③(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0页。
④(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3页。
⑤(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35页。
⑥(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3页。
①(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序言》,《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7页。
②(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页。
③(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1—2页。
④(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72页。
⑤(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2页。
①参见(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2页。
③(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592页。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388页。
⑤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45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65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0页。
①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1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2页。
④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1—172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72页。
②如中国台湾学者王大德直言朱子之心是“气心”,朱子心与理为二,“心具众理”是外在的、关联的“具”。他提出:“主敬涵养之重要性在朱子学中应远不如即物穷理也。故唐先生以主敬涵养为朱子学之第一义工夫显有不妥。在朱子学中,应以即物穷理为第一义,主敬涵养为第二义,随事省察则只能居末也。”王大德:《朱陆异同新论:以‘心与理、心与物’为向度之新综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3、96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形体》(下),第198页。
②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③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④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①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曾亦、郭晓东:《宋明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③曾亦、郭晓东:《宋明理学》,第183页。
④陈林:《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①参见梅彦《朱陆晚年之异初探》,《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
②(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3页。
①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陈林:《朱子晚年工夫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以“已发未发”为中心》,《江淮论坛》2015年第6期。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64—365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65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65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2—193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7页。
③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531页。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534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19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412页。
③参见方旭东《道德实践中的认知、意愿与性格:论程朱对“知而不行”的解释》,《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①(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道一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9页。
②(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056页。余大雅录,朱子49岁。见《朱子语类·朱子语录姓氏》,第13页。
③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54页。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55页。
⑤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⑥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43页。
③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44页。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46页。
⑤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55页。
⑥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6页。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1页。
②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2页。
③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2页。
④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4页。
⑤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21页。
①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75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二),第476页。
③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630页。
①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②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第133—134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501页。
①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3页。
②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0页。
①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②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③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④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639页。
⑤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0页。
⑥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1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7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446页。
③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440页。
④(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廖子晦》,《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册,第2098页。后有校勘言:“‘既竭吾才’,工夫深而力到也。‘如有所立卓尔’,诚之形而行之著也”乃为工夫之境界。(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44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50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80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83页。
①陈建以朱子40岁前为早年,认为“朱子早年出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至中年后始觉其非,而返之正也”。以朱子45岁朱陆相识为标志,将45—55岁定为中年朱陆疑信相半阶段。以朱子56岁时《与刘子澄书》为标志,认为是朱陆晚年相异的开始。(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116、123、130页。
②李绂说:“今按朱子得年七十一岁,定以三十岁以前为早年,以三十一岁至五十岁为中年,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1页。
③王懋竑以朱子46岁编订《近思录》为标志作为第二卷开始,以53岁为第三卷开始,以61岁为第四卷开始。又以“晚与门弟子究悉精蕴”为第四卷之题,似以朱子61岁后为晚年。(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781、597—598页。
①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③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⑤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0页。
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⑦陈荣捷:《朱熹》,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7页。
⑧陈荣捷:《朱熹》,第125页。
①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③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④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⑤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⑥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⑦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⑪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4页。
⑬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40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60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60页。
③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页。
④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中和旧说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4页。
⑦(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万历刊本朱子文集大全序》,《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71页。
⑧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56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71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71页。
④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61页。
⑤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统计。
⑥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40页。
⑦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60页。
①(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876—877页。
②参见(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林择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册。
③(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877页。
④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60页。
⑤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60页。
⑥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8页。
⑦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72—173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②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2页。
⑦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2页。
⑧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⑪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⑫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⑬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⑭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⑮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⑯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①参见(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82页。
③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万历刊本朱子文集大全叙》,《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71页。
⑥陈荣捷:《朱熹》,第135—136页。
⑦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390页。
⑧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⑨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⑪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321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③(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41页。万人杰录,朱子51岁后。见《朱子语类》,第15页。
④(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任伯起》,《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29页。1182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12页。
⑤(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7页。118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54页。
⑥(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07页。118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56页。
①(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詹帅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205—1206页。118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46页。
②(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7—2328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69页。
③(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8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69页。
④(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董叔重》,《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49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69页。
⑤(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周叔谨》,《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54页。118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70页。
⑥(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49页。1188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89页。
①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621页。
⑥(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道一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54页。
⑦参见(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刘子澄》,《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册。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35页。
⑧参见(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学蔀通辨》,《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⑨(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第1页。
①(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年谱》,《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781页。
②(明)程政敏等撰,吴长庚编:《朱子晚年全论》,《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第597—598页。
③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万历刊本朱子文集大全叙》,《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71—5072页。
②(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李守约》,《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04页。1189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01页。
③(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张元德》,《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81页。1190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22页。
④(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张元德》,《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82页。1190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22页。
⑤(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郑子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81页。1191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41页。
⑥(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郑子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83页。1191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41页。
①(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黄直卿》,《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48页。1191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48页。
②束景南按:“朱熹于《四书集注》,晚年多有言及南康本者。”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下),第1064页。
③(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吴伯丰》,《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40页。1194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73页。
④(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吴伯丰》,《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42页。1195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92页。
⑤(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孙敬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63页。1195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03页。
⑥(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孙敬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64—3065页。1196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24页。
⑦(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万正淳》,《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89页。1197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36页。
⑧(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答刘季章》,《朱子全书》,第22册,第2494页。1199年。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493页。
①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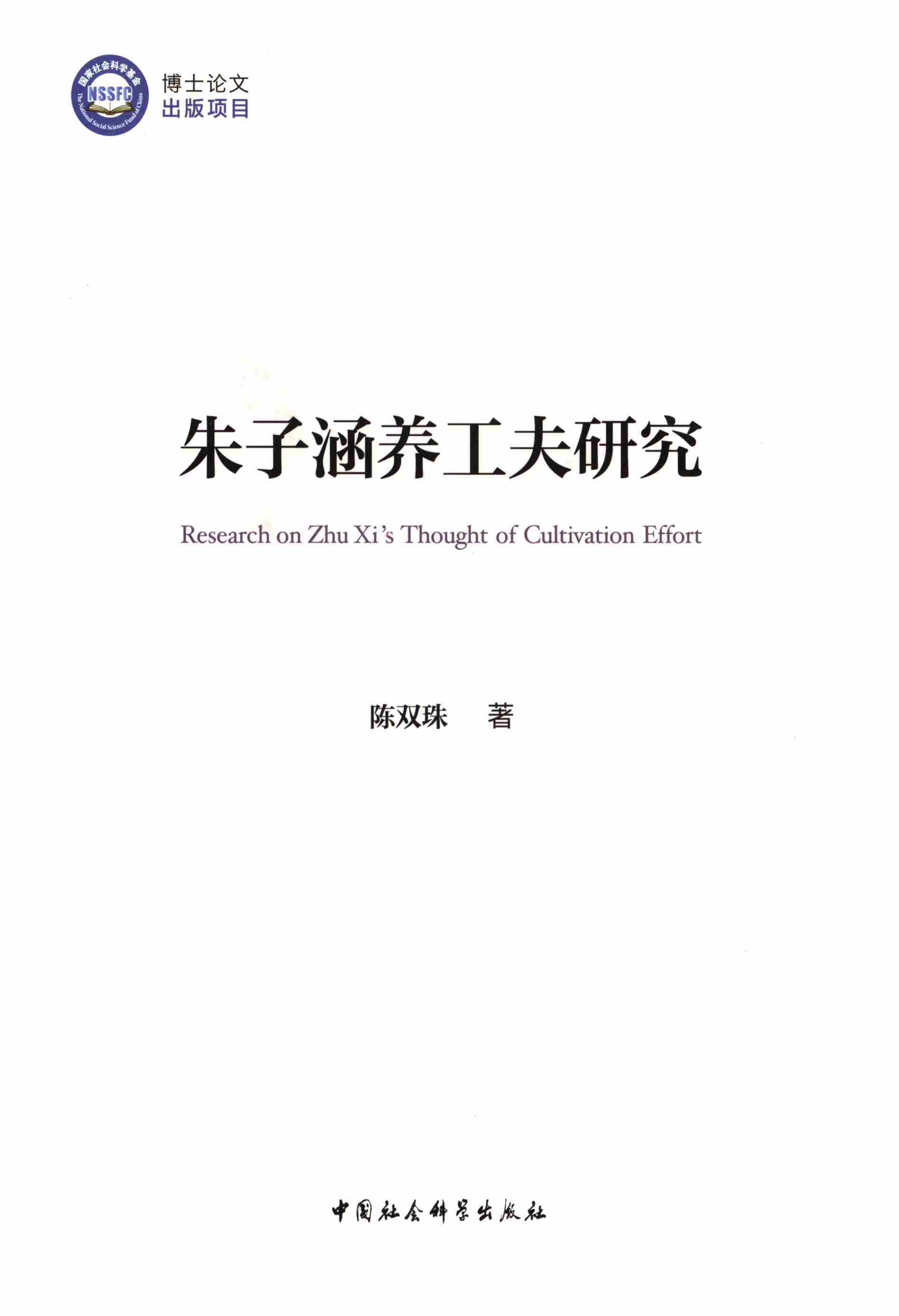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以朱子涵养工夫为研究对象,将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分为中年、中晚年、晚年三个阶段,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和发展历程。全书围绕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涵养工夫内在的关系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三个角度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了考察;从脉络发展的视野厘清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和思想地位;从学术史论辩的视野探寻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从工夫论的确立到完善的动态考察探求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背后的心性论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从而对朱子的修身涵养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研究,也对学术史上关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诸多判定和争议进行了检查。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