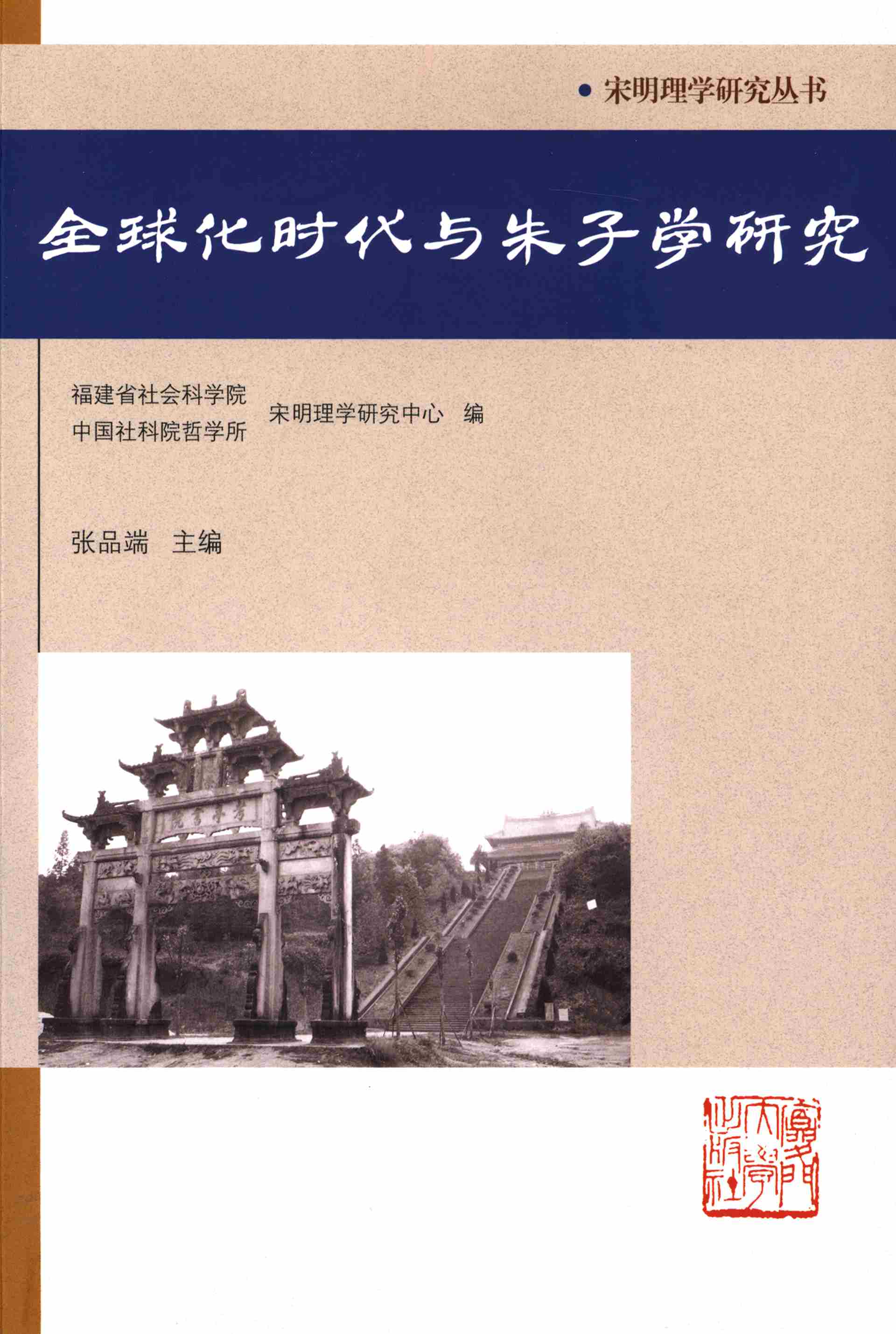(三)“义”的性质与实践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211 |
| 颗粒名称: | (三)“义”的性质与实践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3 |
| 页码: | 127-129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儒家思想中的“义”既包含形上的理学意味,又强调现实实践中的智慧。朱熹主张“仇者以义解之”,强调解决矛盾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该理念在当代社会仍具启示意义。 |
| 关键词: | 朱熹 家训 仇怨 |
内容
孔子所讲的“以直报怨”,强调的是根据正当性原则,将“怨”解决于激烈与公开的冲突发生之前。这一原则有一明确的现实依据,那便是具有一定自然法意义的礼。春秋公羊学和礼学中所阐扬的“复仇”理念,是在特殊的情境中为了维护宗法伦理与宗法制度所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可以说是“以直报怨”的极端化延续,其终极目的乃是“以杀止杀”,以维护作为社会体系最高价值的“和”。当然,这也是“仇必和而解”的一种极端化表现,其不仅同样属于礼的范畴,更是上升到了“义”的层面。
在早期的社会观念体系中,礼、法之间的畛域并不分明,礼作为宗法伦理的成文规范与意义象征,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①。因此以礼代法是较为普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律法,尤其是儒家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中的律法,对于《周礼》《礼记》与公羊春秋学所宣扬的通过“复仇”来维护社会的“自然公正”的行为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但是随着时移世易,社会法制体系愈显发达,礼、法在形式与功能上的界分愈发明确②,因复仇而杀人越来越受到律法的限禁。既然通过“复仇”以维系宗法伦理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行为,其合法性慢慢受到了质疑,这一原本“合礼”的行为就必然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此即《礼记·礼运》所强调的礼“以义起”。
对于“义”,朱熹一方面视“义”为天理的运动流行法则,赋予其理学的形上意味,说:“义者,天理之所宜。”③另一方面,朱熹又强调“礼即理”,认为礼是天理的现实体现与实践,因而“义之所在,礼有时而变”①。要求在礼的具体实践中“酌其中制,适古今之宜”②,以“义”的辩证之道通达礼的古今之变。所以朱熹对“仇”的解决求之以“义”,要求“仇者以义解之”,就是既强调了对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并不限于宗法伦理)的维护,也强调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辩证智慧,乃道德准则与实践智慧的统一,实为“大复仇”与“仇必和而解”两种理论的会通。因此,相比“直”来说,“义”一方面与“直”一样,同属于儒家伦理中的正义与正当范畴。另一方面又更是对“直”所代表和依据的确定性规则(即“礼”)在具体实践中的超越、升华与完善③,正如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指出:“……在这些情形下,现存的法律不能提供任何清楚的答案,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答案。在这些境况中,法官也缺少规则,也必须运用理智,如同立法者当初一样……就只能以某种方式超出已有的规则……这就是任何一位明智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必须随时依实际情况而具体实例化。这不仅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把各种美德充分地具体实例化。”④这段话即可视作是对儒家之“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运用的直白浅近的阐释。
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科技日新月异,在人们的生活日渐便捷富裕的同时,面临的压力却也越来越大。在高强度的竞争与快节奏的生活中,人际间的矛盾往往难以避免,甚至显得更加复杂。朱熹在《家训》中主张“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其中所体现出的传统儒学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及解决矛盾的富于辩证色彩的方法论智慧,在今天无疑仍有着较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怨者以直解之”主张不要“匿怨”,将心中对他人的不满与怨恚,“当报则报,不当则止”,强调以正当和坦直的方式予以及时解决。如此既能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也保障了个体的心理健康。而与之相关的“以怨抱怨”易陷于人际矛盾的恶性循环中,“以德报怨”又无法成为常态。“仇者以义解之”则告诫我们面对既成的、较为强烈和明确的仇恨,不仅要更为慎重地考虑解决仇恨的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也要充分考虑手段的有效性。而最终的目的,便是仇恨的合乎情理的解决,其实质实乃充满辩证智慧的“仇必和而解”。总之,“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核心精神都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道消弭矛盾,归根结底,仍不过是一个“和”字。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都是如此。
在早期的社会观念体系中,礼、法之间的畛域并不分明,礼作为宗法伦理的成文规范与意义象征,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①。因此以礼代法是较为普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律法,尤其是儒家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中的律法,对于《周礼》《礼记》与公羊春秋学所宣扬的通过“复仇”来维护社会的“自然公正”的行为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但是随着时移世易,社会法制体系愈显发达,礼、法在形式与功能上的界分愈发明确②,因复仇而杀人越来越受到律法的限禁。既然通过“复仇”以维系宗法伦理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行为,其合法性慢慢受到了质疑,这一原本“合礼”的行为就必然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此即《礼记·礼运》所强调的礼“以义起”。
对于“义”,朱熹一方面视“义”为天理的运动流行法则,赋予其理学的形上意味,说:“义者,天理之所宜。”③另一方面,朱熹又强调“礼即理”,认为礼是天理的现实体现与实践,因而“义之所在,礼有时而变”①。要求在礼的具体实践中“酌其中制,适古今之宜”②,以“义”的辩证之道通达礼的古今之变。所以朱熹对“仇”的解决求之以“义”,要求“仇者以义解之”,就是既强调了对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并不限于宗法伦理)的维护,也强调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辩证智慧,乃道德准则与实践智慧的统一,实为“大复仇”与“仇必和而解”两种理论的会通。因此,相比“直”来说,“义”一方面与“直”一样,同属于儒家伦理中的正义与正当范畴。另一方面又更是对“直”所代表和依据的确定性规则(即“礼”)在具体实践中的超越、升华与完善③,正如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指出:“……在这些情形下,现存的法律不能提供任何清楚的答案,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答案。在这些境况中,法官也缺少规则,也必须运用理智,如同立法者当初一样……就只能以某种方式超出已有的规则……这就是任何一位明智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必须随时依实际情况而具体实例化。这不仅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把各种美德充分地具体实例化。”④这段话即可视作是对儒家之“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运用的直白浅近的阐释。
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科技日新月异,在人们的生活日渐便捷富裕的同时,面临的压力却也越来越大。在高强度的竞争与快节奏的生活中,人际间的矛盾往往难以避免,甚至显得更加复杂。朱熹在《家训》中主张“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其中所体现出的传统儒学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及解决矛盾的富于辩证色彩的方法论智慧,在今天无疑仍有着较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怨者以直解之”主张不要“匿怨”,将心中对他人的不满与怨恚,“当报则报,不当则止”,强调以正当和坦直的方式予以及时解决。如此既能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也保障了个体的心理健康。而与之相关的“以怨抱怨”易陷于人际矛盾的恶性循环中,“以德报怨”又无法成为常态。“仇者以义解之”则告诫我们面对既成的、较为强烈和明确的仇恨,不仅要更为慎重地考虑解决仇恨的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也要充分考虑手段的有效性。而最终的目的,便是仇恨的合乎情理的解决,其实质实乃充满辩证智慧的“仇必和而解”。总之,“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核心精神都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道消弭矛盾,归根结底,仍不过是一个“和”字。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都是如此。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