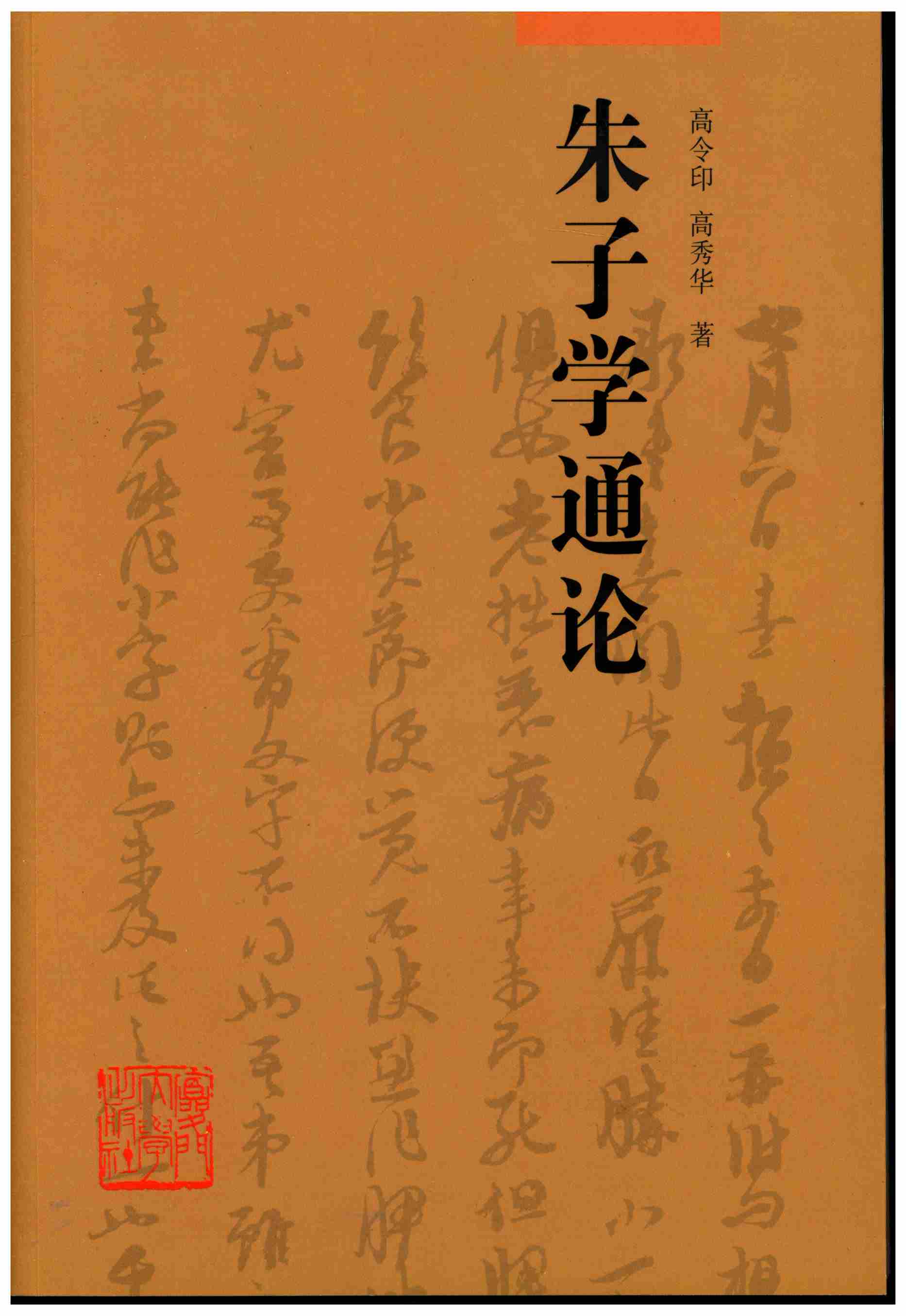内容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
一 由闽中而全国
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闽学)是闽中之学,是与濂、洛、关等之学相并称的地域性的理学学派。但是,由于它在创立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被统治者所认识,很快由初期活动的闽、浙、赣地区而全国,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前面讲到,朱熹在世时福建朱子学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数百名朱熹门人分别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在“庆元党禁”时期和朱熹死后,他们大都返回原籍,在全国各地传播朱子学。清人黄百家在论到朱熹浙江崇德籍门人辅广传播朱子学的情况时说:
所传之学,蜀则有魏鹤山了翁;闽则有熊勿轩禾、陈石堂普;吾东浙,
自韩恂斋翼甫传子庄节性、余端臣,再传而有黄文洁震。①这就是说,辅广通过四川的魏了翁、浙江的韩翼甫及其子韩性、余端臣、黄震,把朱子学传至四川、浙江。对于魏了翁,据记载:
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②
李燔是江西永修籍朱熹门人。李燔除把朱子学传给魏了翁外,还亲自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传播朱子学。据记载:
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按即今湖南岳阳),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禀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改襄阳府(按今属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属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①
非福建籍的朱熹门人大都像辅广、李燔这样在各地传播朱子学,从而朱子学流传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朱子学系,如江西系、浙江系等。
在朱熹门人传播朱子学的过程中,福建籍朱熹门人黄榦居首要地位。他以得朱熹遗命自任,以墨子辟杨墨自励,呼喊着“卫道岂可以不严乎”。他曾讲学于江西庐山白鹿书院,“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邦寺以处之”。②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此叙朱子学由宋而元,路线分明。全国各地初传之朱子学,大多出于黄榦之门。黄榦曾知江西临川。浙江金华人何基之父为临川主簿,命何基师事黄榦。黄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悚惕受命”。金华人王柏闻何基从学黄榦得朱子学之正传,乃往学于何基,何基告以“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④金华金履祥从学王柏、何基,得朱子学真传。金华人许谦又受学于金履祥。此所谓“金华四先生”皆出黄榦之门,“推源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⑤朱子学盛行于浙江,实黄榦之力也。
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其地饶鲁(号双峰)从其学。因此,“双峰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①全祖望说:
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子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按程若庸),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合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终近乎朱。②
这就是元代江西朱子学之源流,亦是以黄榦为纽带。
朱子学流传于北方,与黄榦曾知德安(今湖北汉阳)有关。窦默避元兵逃至德安,县令以程朱性理之书予之,可知黄榦把朱子学传至德安。③后来,元兵入侵德安。杨维中为大将军,其幕僚有姚枢从俘虏中求儒者数十人,其中有赵复等人,带自燕京(今北京),建太极书院,由赵复等人讲学,授程朱所著与其诸经传注,门徒数百人。此亦知赵复等人之学亦是在德安由黄榦所传。朱子学传之北方自此始。姚枢在北方刊朱熹《论孟或问》、《小学》等书。其后,姚枢居辉县(今属河南)苏门,河南沁阳许衡至,尽录程朱传注以归。上述杨惟中、窦默、姚枢、赵复、许衡等,皆是元初名儒。可见,北方朱子学之传播,亦渊源于黄榦。
对于朱熹门人和再传门人传播福建朱子学和福建朱子学流传的情况,清人蒋垣有概括的叙述。他说:
朱门受业为多,最知名者黄榦、李燔、张治、陈淳、李方子、黄颢、蔡沉、辅广等。而黄榦门人最多,潘柄、杨复、陈宏、何基、饶鲁皆其高弟。基传之王柏,柏传之金履祥,履祥传之许谦,饶鲁传之吴中行,中行传之朱公迁。时与朱熹同任道学者吕祖谦、张栻。祖谦受业于侯官林之奇。当时杨、胡、林、朱、黄、蔡之学盛行于江之东南。张拭,成都锦竹人。至宗、宁间,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辅广、李燔之学授教生徒,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则闽学传之西蜀矣!理宗时,杨惟中建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又姚枢隐居苏门,以道学自任,刊《小学》、“四书”,及蔡氏《书传》、胡氏《春秋传》,而闽学至于河溯矣!此八闽道学(理学)源流之大概也。④
河溯(朔),泛指黄河以北。《书·泰誓中》有“王次于河朔”之语,孔传谓“渡(黄)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由此可见,闽学传播至全国。清人张伯行在《道南源委·序》中说: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子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①
到了明清时代,福建朱子学学者还致力于把闽学往外省传播。例如,清初福建人龚景瀚在关中、李光地在河北河南、蔡世远在江浙、蓝鼎元在广东台湾、阮旻锡在山东、林嗣环在海南岛、黄志璋在广西两湖、林之浚在云南贵州、朱兆纲在山西安徽、吴鸿锡在四川等,传播朱子学。
据以上诸家论述,朱子学由闽中而全国的大概情况如下:
二 国家的正宗思想
随着朱子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全国传播,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它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早在朱熹死后的第二年(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十月,宁宗皇帝就下诏赐谥,除朱熹“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②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十月,诏赐谥朱熹曰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理宗皇帝在封制中谓,朱熹遗著“有补于治道”。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理宗皇帝谓,“深有不同时之恨。每阅‘四书’之奥旨,允为庶政之良矩”。①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宗皇帝诏学宫列朱子从祀庙堂。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复科举,诏定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诏建朱子祠,“立徽国文公之庙”。②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皇帝命礼部传谕规定: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需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③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朱熹、真德秀等福建朱子学学者的经典注疏。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康熙皇帝先后谕敕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编辑《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由上可见,在南宋末和元、明、清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成为法定的教科书,是学者必读的课本,文官考试不出朱子学界限。朱子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在朱子学控制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七八百年中,其渗透到思想意识的各个领域之中。近代著名的福建籍学者严复说:“吾侪今日(按19世纪末)思想、风俗、政治,直接间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④“籀”即归纳推理。意思是说,宋元明时代的思想意识都渊源于程朱理学,而集理学之大成的朱子学(闽学)即发源于福建。
第二节 全国的派别和衍变
一 衍变的内在倾向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差不多又经过了三四十年,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就遍及全国。朱子学在福建的传衍和分化是个雏型,全国朱子学的派别和衍变是其在福建传衍和分化的扩大和发展。
由于朱熹综罗百代、集诸儒学之大成,非某个后继者所能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集大成,体系庞大,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对全国朱子学衍变的内在倾向,今人蒙培元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说:
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个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论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①
蒙培元对南宋末、元、明时代哪个朱子学家属于哪一哲学倾向,以及按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其这里的概括说明是很确切的,为研究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提供了指导性线索。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成为整个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根据理论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进行衍化。基于上述黄榦是朱子学由闽至全国的桥梁,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是在黄榦思想中开其端的。黄榦固守师说,只是在体之用上有所阐发。南宋末黄震曰:
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②
这里黄震叙述了黄榦思想与朱熹思想之不同,在黄榦思想中就埋下朱子学日后分化的根苗。体用关系体现为理一分殊,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人的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孟子的四端说来说明道德的体用关系。黄榦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③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道德之体,有此体必然表现为与此体相联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道德之实践(用);抽象的天理世俗化,为人人得以遵循的道德准则,通过格物明理实现人内心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善;实际上,格物明理和明内心的道德之善是对立的。这是黄榦哲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
朱子学于元初盛行于全国之后,其衍化大致有三派:一是以赵复、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派,一是以何基、许谦为代表的浙江金华北山学派,一是以饶鲁、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广汉双峰学派。这三派大致按上述黄榦思想中的三种倾向进行衍变和分化,走向不同的学术道路,因而使朱子学原来理论上的裂痕走向解体的道路。
朱熹思想的解体和分化促使朱子学的演进,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本身的发展必然会解体和分化,同时其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其后一二个后继者所能继承和发展的。南宋至明朝末年,朱熹思想向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两种方向发展的结果。最后出现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和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都是从朱熹思想体系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由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中国社会由古代孕育着近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朱熹,其内圣成德达到了成熟和综合点,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即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的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时期,西方社会也正开始近代化,出现“文艺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是与西方同步的,或者说早于西方。牟宗三在讲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时,深刻指出:
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300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民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200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向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
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①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他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理想往前发展,推翻清王朝,开出一个外王事功的大时代,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
二 黄震 金华四先生
南宋末年浙江朱子学有辅广系黄震、黄榦系金华四先生等。对此,《宋元学案》有所综合评述。其曰:
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平生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即江西)诸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子(金华四先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折衷诸儒,即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②
浙江的朱子学,对朱熹的思想,黄震有较大的修正,金华四先生则是墨守朱熹家法,因此分开论述。
黄震(约1213—1280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浙江慈溪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官吴县、华亭县、长洲县尉,史馆校阅,广协、绍兴通判,抚州知府,江西、浙东提举常平等。宋亡后,“日惟一食,仰天长恨,祈速死”,最终“饿于宝幢而卒”③。其著作有《黄氏日抄》(即《慈湖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仰天遗草》等。
黄震对天理的论述,基本上与朱熹同。而在讲到理与道的关系时却对朱熹有所修正。如黄震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④
黄震强调,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这跟朱熹的讲法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理,是人道;作为万物本原的理,是天道,而天之道则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外的。这就对朱熹之“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所修正。由此,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之“道不必贯而本一”的观点。他说:
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①
他认为,朱熹后学“舍孝弟忠信不讲而独讲一贯”②的倾向,是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论的断章取义,是道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点。
黄震认为,朱熹等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是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不一致的。他说:
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③
他认为,“性相近”包括了气质和天地之性,而不是朱熹等所说的只是“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哪里有三品来?”④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性三品是指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没有三品的问题。对此,黄震说:
性有三品之说,正从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来,于理无毫发之背。至伊、洛添气质之说,又较精微。盖风气日开,议论日精,得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对说,而后孟子专指性善之说举以属之天地之性,其说方使无偏。此于孟子之说有功而于孔子之说无伤。实则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言。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说本于上智、下愚之说,而后进喜闻伊、洛近日之说,或至攻诋昌黎耶?⑤
在黄震看来,韩愈之性三品说,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二程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致的,而朱熹却说性三品不包括天地之性,不是相矛盾吗?
在知行问题上,黄震强调躬行。他说:
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盖论说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曾用力于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说?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见言晦翁之学者几人,往往不知其躬行。
……世所谓《中庸》、《大学》者,身未必行,惟见笔舍华靡。①
在这里,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笔舌华靡”的空谈义理、不知躬行的行为。
由上可见,黄震对朱熹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所立异的。因此,黄震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不仅有继承,也是有所发展的,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
金华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学者称北山先生)及其弟子王柏(1192—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柏弟子金履祥(1232—1303年,又名祥、开祥,字吉父,号次农,因家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祥弟子许谦(1270—1337年,字益子,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是朱子学浙江金华之主要传人,被朝廷列为朱子学的正宗。《宋元学案》专立《北山四先生学案》,详述其朱子学思想。
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严守朱子学门户,强调读书传览为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何基语录》说:
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②
他们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寸步不离,确守师说。清初黄宗羲说: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③
北山学派由确守师说,只注重读书穷理,继承和发挥朱子学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虽然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但是由于走向章句训诂的道路,使朱子学变成烦琐哲学,没有开辟出新的境界。特别是其中的王柏,他的《诗疑》、《书疑》,原是对朱熹《诗集传》的继承,却走向极端,偏离了儒学正统,受到后世朱子学者的批评。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更觉朱子学正统派的空言无实。清代前期,虽有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及其他理学名臣大倡朱子学,使其一时兴盛;清末有朱次琦(1807—1881年,广东南海人)、杨昌济(1871—1920年,湖南长沙人)、辜鸿铭(1897—1928年,福建厦门人)等人提出重整朱子学,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和朱次琦同时的文廷式(光绪帝珍妃的老师)曾谓朱熹“训门人语多痛切,数十世后如见其人”。①朱次琦提出“朱子百世之师”,朱子“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②
杨昌济曾先后留学日、英、德等国9年。他在五四运动前期的中西哲学论争中,采取调和折衷态度,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实际上他立足于程朱理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讲授伦理学。他说:
所谓不限于西洋之理论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③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学应为体(正宗),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应尊为儒家思想的典范。他为讲授伦理学而编写的《论语类钞》共38条,其中有朱熹语录释《论语》者达22条,占三分之二。如第22条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首先就引用了朱熹一大段语录,即: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道,譬则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就是说,太极(道之体、一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万殊各得其所”就是太极(道之体、一本)的体现或作用。这段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典型表述,杨昌济解释说:
宇宙为一全体(即一本、太极),宇宙间所有一切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同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
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熹下列一段话,其曰:“吾子之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有见者也。”⑤杨昌济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来论证如何积累知识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此外,杨昌济还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吸取和发扬朱子学。
由上可见,直到清末和民初,朱子学正统派在一些学者中和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就全国来说,朱子学终未能真正恢复其元气,在理论上未有多大进展,而且趋于终结,这就是由自我窒息而后日趋沉寂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三 双峰学派 饶鲁 吴澄
《宋元学案》谓,黄榦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江右即江西,其代表者为双峰学派之饶鲁、吴澄等。“双峰(饶鲁)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吴澄)”,其学术活动时期为宋末元初。
饶鲁(生卒不详),字伯舆、仲元,号双峰,江西余干人。据载,“庚申(1206年),诏饶州布衣饶鲁,不事科举,一意经学,补迪功郎、饶州教授”①。其著作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学庸纂述》、《西铭录》、《近思录注》等。
对于饶鲁之朱子学,有谓不拘于章句,一如朱子之于二程,“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②。可知饶鲁不是墨守朱熹门户的。饶鲁认为,理气不相离,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气为理之衬贴。他说:
“浩然之气”,全靠道义在这里面做骨子。无这道义,气便软弱。盖缘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理是气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气。以有太极在底面做主,所以它底凭地浩然。③
这里全是朱熹之理气关系的说法。他又说:
“发育万物”,以道之功用而言,万物发生长育于阴阳五行之气,道即阴阳五行之理。是气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极于天”,以道之体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无过于天者。天之所以为天,虽不过阴阳五行浑沦磅礴之气。而有是气,必具是理。是气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全体大用,极于至大而无外有如此者。④
此是说理气相即不二。这里还讲了道的体用关系,即其所谓“道之体段”、“道之功用”。道是弥沦天地的,是主宰天地之气的。
饶鲁继而认为人道的极则是天理。他从性为人所禀之天理出发,发挥了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观点。他在疏解张载的《西铭》时说:
《西铭》一书,规模宏大而条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尽。然其大旨,不过中分为两节。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后一节言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何谓人为天地之子?盖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是性,犹子受父母之气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举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为大父母。故以人而观天地,常漠然与己如不相关。人与天地既漠然如不相关,则其所存所发宜乎?①
由此,他得出:“言天以至健而始万物,则父之道也;地以至顺而成万物,则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间,禀天地之气以为形,而怀天地之理以为性,岂非学之道乎?”他把天人地释为父子母,是有新意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生,是天地之气以为形,天地之理以为性,故天地与人,犹如父母之与子。因而天地与我一体,即他所说的“物吾党与”。
饶鲁进一步指出,人本身具有善端,人都有自新的欲望,即所谓民之心本自好善而恶恶,熟不欲自新?因为,仁即心,心之存即是识仁而成仁心。他说:
诚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颜子问仁,夫子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紧要在四个“勿”字上。仁属心,视、听、言、动属身,“勿”与“不勿”属意。若能“勿”时,则身之视、听、言、动便合礼,而心之仁则存,以此见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在意之诚不诚。所以,《中庸》、《孟子》只说“诚身”便贯了。②
这里的说法与朱熹之心统性情说不同。在朱熹那里,人禀受天道为性,故性具天理;心不等于性,故心不等于天理。而饶鲁却认为,心即仁,故仁同于天理。这同陆九渊的“心即理”相似。在饶鲁看来,心之能存与否,全在身之视、听、言、动,而视、听、言、动又在于“意之诚不诚”,故“诚”就将诚意、正心、修身三事贯串起来。诚即无妄、不自欺意。
饶鲁提出以敬为诚的存养省察工夫。由此他喜欢静坐。他说:静坐时,须心主于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言于敬,亦静坐不得。心是个活的物,若无所用,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圣人说“难矣哉”,意甚该涵。③
他认为,通过静坐,就能收敛“野马”之心,使本来的善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禅家的“修心”、“守心”相类似。
上面讲的居敬,只是饶鲁为学之一。他认为,为学四方,即立志、居敬、穷理、反省。①他的为学之方由“立志”始,然后居敬、穷理,而终止于反身。这是内外结合的方法,是符合理学家的“涵养须用敬,进德在致知”的原则的。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历官元朝之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制诰、集贤殿直学士等。著有《五经纂言》、《皇极经世续书》、《道统图》等,清人辑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文正公外集》。
在元代,吴澄与许衡为名儒。许是北方人,于元初“粗迹”朱子学。吴是南方人,直承朱子学大家,是“正学真传”。因此,元代朱子学有“南吴北许”之称。
吴澄以朱熹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其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享,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②
这段话值得注意者,一是韩愈论道始于尧舜,而吴澄则据董仲舒意谓道始于天,此说出了宋明儒的本体论。二是其用《周易》之元、亨、利、贞把历史顺序规定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每一段又分元、亨、利、贞。三是他把朱熹说成是“利”,而不是终结“贞”,一方面他不把朱熹看成为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似乎把自己看成是“贞”的地位,以跻身宋儒诸子的继承者之列。所以,上引《元史》本传接着谓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吴澄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是对朱熹的经学有较大的补充和发挥。他的《五经纂言》,实际上完成了朱熹的未竟之业。朱熹曾与吕祖谦等商议编次“三礼”,而终老未及为。朱熹曾说:
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于本经之下。③
但是,朱熹只留下草创本《仪礼经传通解》。后来,黄榦等也曾治礼,没有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吴澄从中年到晚年,几乎倾一生精力,完成《五经纂言》,实现了朱熹的未竟之业。他在《诸经序说》中说:
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仪礼)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稿,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夫以《易》、《诗》、《书》、《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其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①
吴澄“辄因”朱熹筹画之意,以《仪礼》十七篇为经,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例,将《礼记》(大小戴记和郑注)分类编次,纂成《仪礼逸经》八篇。就是把《礼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礼记》中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此二篇并与《小戴礼记》相参校),又把郑玄《三礼注》中的《中霤》、《禘于太庙》、《五居明堂》,共成二卷八篇。另外,又将大、小戴记中的《冠仪》、《昏仪》等八篇,和《礼记》中的《乡射仪》、《大射仪》二篇,辑成《仪礼传》十篇。这样,吴澄把汉以来流传的《礼记》(大小戴记,以至郑玄《三礼注》等)肢解,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这不仅完成了朱熹生前的夙愿,而且经过这样的整理,使流传千百年来“难读”的一部《仪礼》,得见崖略,诚是经学史上的一大贡献。②
吴澄治五经不守朱子学门户。如其《易纂言》,自称“用功至久,皆自得于心,有功于世为最大”③。在这部《易》学中,就有和会朱陆的地方。
在本体论上,吴澄认为太极即道。他说:
所谓极也,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④
“太极”所以能起主宰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含有动静之理,它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如人之乘马,人随马的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它“常常如此,始终一般,无增无减,无分无合”。所以太极尽管包含动静之理,而主宰世界的生成、变化,它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⑤
吴澄进一步把太极说成是理、天理,而把理、天理释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者。他说:
气之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气之往来屈伸而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命各虽殊,其实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①
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②
太极与理的关系,就宇宙本原来说是太极,就宇宙化生二气五行以至万物的过程来说是理。这样,理就是万物所以形成的理,而太极就是理的全体。万物中具体的理与本原的太极是万理一原的关系。所以,整个世界由它的本原到化生万事万物的现象界,都是由于太极和理的一系列的作用。
吴澄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太极,是人道的极则,也就是天理。那么,人是如何去认识它呢?是从吾心去体认,还是从万物去参究呢?是立之于本心,还是格之于外物呢?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在朱、陆之后,吴澄则是“和会”两家之说,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方法。
在吴澄看来,湛然纯善的天地之性附于人的时候,随着各人气质的清浊不同,而有善恶之分,因而有了气质之性。但是,即使是那些因气浊而恶的人,其天地之性亦在“其中”,只是“拘碍沦染”于浊气而已。悬之于高远的天地之性,不仅予性善的人,而且也予性恶的人。这就给具有气质之性的那些恶与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他说:
人之明德,即天所以与我之明命也,自天所赋于人而言而谓之命,自人所得于天而言则谓之德,其实则一而已。然常人为气禀物欲之所昏,而不察乎此,是以昏昧蔽塞不能自明,至于梏其性而忘之也。故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所以与我之明德而有察焉,则必然因其所发,而致其学问思辨推究之功,又能因其所明,而致其存养省察推行之实,则吾之明德,亦得以充其本体之全,以无气质物欲之累,而能明其大德与尧无异矣。③
在吴澄看来,“明其德”不是由身外格物以明理,而是求之于己,自明其心。故他自己概括其方法为“自新”。可见,他主张自省自思而达到自觉,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相违背的,而与心学派明心穷理却是接近的。
吴澄认为,自省自思而自觉即是诚与敬。他说:“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①他又说:
凡所应接,皆当主于一心,主于一,则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处自无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积久,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②黄直卿(榦)谓敬字之义,近于畏者,最切于己。凡一念之发,一事之动,必思之曰:此天理抑与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则不敢为,惴惴儆慎,无或有慢忽之心,其为之敬也。③
吴澄所谓敬,就是在“一念之发,一事之动”时皆以天理来约束思维;凡一念一事,都要想一想这是天理还是人欲。他完全排除了外物之诱惑。先秦思孟学派提出“诚者天之道”,是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人道的极则。人能“思诚”即可达于“天之道”的诚。④吴澄所谓“思诚”,就是思我心中固有的诚。他说:
人之初生,已知爱其亲,此实心自幼而有者,所谓诚也。爱亲,仁也。充之而为义、为礼、为智,皆诚也,而仁之实足以该之。然幼而有是实心,长而不能行,何也?夫诚也者,与生俱生,无时不然也,其弗能有者,弗思焉尔。五官之主曰思……所以复其真实固有之诚也。⑤
他把诚说成是与生俱来,自幼而有。诚的内容就是爱其亲,也就是仁,它充实显露之后就是义、礼、智。在吴澄看来,它是具体的,并非是悬之于心外的一种神秘境界。而要保持自幼而有的诚,就是思。所谓思,就是去其恶欲和复性的冥悟过程。这样,就是去掉“人欲”,以达到所谓真实“不妄”、“不自欺”。由此进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的道德之善走过来的,反对单纯读书明理,强调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双峰语录》有说:
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⑥
在饶鲁看来,道理须是涵养,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来?可见,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道德之善的思路上往前衍变的,其心学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吴澄的心学思想更加明显。韩国李朝李退溪在讲到吴澄时曰:
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公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①
吴澄对朱熹和陆九渊两家都很推崇,他在《与许左丞书》中认为,“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②。全祖望谓吴澄“固朱学”、“兼主陆学”。③
到了明代,先有吴与弼(1391—1469年,号康斋,江西崇仁人)提出“敬义夹持,明诚两进”④,发明代心学之端;再经陈献章(1428—1500年,号白沙,广东新会白沙里人)而至王阳明,把朱子学衍变为心学。王阳明是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者,即心学从朱子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并与朱子学相对立。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阳明学是理学由烦琐变为简易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启蒙思想的出现而要求冲破朱子学一统天下的结果。阳明学差不多盛行了一百年,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正统派朱子学抬头和王夫之等人战斗的气论实学的出现,王学即告终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 北方学派 许衡
元初朱子学传入北方后,很快就形成为以赵复、许衡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李退溪在讲到赵复时说:
姚公(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公(按指赵复)传其学。由是许公衡、郝公
经、刘公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公始。⑤当时属于北方朱子学派的还有窦默等人。全祖望谓“河北之学传至江汉(赵复)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⑥
这里主要论述许衡。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等。他为元朝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即运用朱子学治国,其朱子学思想被称为道统正脉。他在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期间,向蒙古弟子传播朱子学,使当时学人皆诵习程朱之学,有“以夏变夷”之功。卒赐荣禄大夫,谥文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祀孔庙。
许衡的著作有《大学要略》、《大学直讲》、《稽古千文》等,后辑为《鲁斋遗书》。近年台湾中文出版社据日本宪文九年(1669年)刻本影印出版《鲁斋全书》。
许衡为学,一以朱熹之言为归。实际上,他主要发扬朱熹的心学思想,把朱子学变成以“尊德性”为主的践履之学。他认为,朱熹的著述太多,重点不突出。“许文正公表彰朱子之书,天下乐为简易之说者。”①他沿着“简易”的方向,在朱熹的心说上兜圈子,为后来的心学一派开辟出道路。
许衡认为,人皆“禀天命之性为明德之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与尧舜神明为一”,但是在践履上一般人与尧舜圣人就不同了。他说:
众人多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能长存:或发于一件善念,便有被气禀物欲之私昏蔽了,故临事时对人旋安排把捉;未临事之前,与无人独处,却便放肆为恶。②
此谓善念到临事时就可以检验出来了。他特别强调慎独,在“与无人独处”时亦不能放肆为恶,必须谨慎而不敢疏忽才行。所以,他十分强调《大学》所讲的慎独工夫。他说:
幽暗之中,细微之事,人以为可忽者,殊不知其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更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惧,而于此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虽人所不知,而独知之地,尤必极其谨慎而不敢忽。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③
他强调,“独是自家心里独知处;好善恶恶,实与不实,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
心里独自知道这等去处。君子必要谨慎,以审其几微。”①
在许衡看来,意念未发时之戒慎恐惧,能存天理之本然,其工夫是存养;由存养至慎独,能谨慎己所独知,从而遏人欲于将萌以至方萌。其工夫是省察。他说: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执之不使变迁。如此,则应物无少差谬。此所谓致知也,省察之事也。②
如能时时内自省察,无有不善,就能无愧于心。慎独是省察的前提和基础。气禀物欲之拘蔽于人既不容忽,人的尽心工夫就会连续不断,性中本然之理(善)即能永存。
许衡进一步指出,持敬则能身心收敛,身心常存。他说: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少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日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礼记》一书近千万言,最后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从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恶,皆从不敬上生。……这一件先能着力,然后可以论学。③
他所讲的这些,就是朱熹所讲的收摄涵养此心,敬之以恒,敬之忽失,就是常惺惺法,提心吊胆,便心不失其正。
在许衡看来,慎独为省察,持敬为涵养。在省察与涵养间他又加了个格物致知,这是许衡心学之独到处。他明确提出,“知其性是格物”④。此性是心体之性。知此心体之性,非格物不可。他说: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此解说个“穷”字;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说个“理”字。所以然者是本然也;所当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当然者是义也。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⑤
理固然为心体所内具,通过格物穷旭,如能自显心体所本具之理,此理即人之性。由知物之所当然,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物之所以然是其所当然之理由,此理由人于当初所未知。通过格物而致知。
由上可知许衡之心学体系了。他的结论是心与理为一。据记载:
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如何?先生曰:便是一以贯之。再问:理出于天,天出于理?先生曰: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①
由此,他便得出人、物后之于理的结论。他说:
有是理而后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诚有是理,而后成木之一物。表里粗细无不到,如成果实相似,如水之流满出东西南北,皆可体力而用行。积实于中,发理于外,则于恻隐、于羞恶,内无不实,而外自无不应。凡物之生,心得此理而后有形,无理则无形。②
由上可见,许衡为学皆朱子之义理,其特点是强调践履工夫,使心性真正体现于天理之中,达到完善的人格境界。所以,把许衡之学视为求心之学。
五 由郝经到王夫之
上述由黄榦开其端的朱子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在元代北方朱子学学派中都可以找到代表人物。元明北方朱子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思想基础,但是,北方朱子学派呈现出了朱子学中气论实学的思想倾向。当时北方朱子学派中的郝经、刘因等代表了这种倾向。
郝经(1223—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著《续后汉书》、《陵川集》等。早年“搜览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③,学问极为渊博。元初,郝经受学姚枢。先是姚枢在燕京(北京)建太极书院,请朱子学家赵复讲学于其中,姚枢得赵复所传;后来姚枢隐居苏门,许衡、郝经、刘因得其书而承其学。但是,郝经与赵复、姚枢的思想有所不同。例如,郝经把太极(理)看作“浑沦”,即看作是物。他在《太极图说》中认为,无极而太极者,包本末,贯隐显,一体用,极始终。他说:
浑沦圆转,而无上下内外,开廓布置而皆上下内外,含弘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混然一大活物,旁行而不流,无所不往而未尝去,居其所而变动无穷焉。圣人无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极。④
郝经这种对太极(理)的界说,就中孕育着气论实学的因素。今人龚道运说:
郝经言道或太极之为生生之理,乃就阴阳之气之生生之所以然而言。此理贯而主乎此生生之气流行中而为其理者,故曰理入于气。抑此理之入乎气,亦可谓其承先之气,以其后之气,而行乎气之中。所谓理不离气,即自理不离其所承之气与所起之气,如位于己化已息之气与方生方起之气之间而言耳。①
郝经对理气关系的认识含有二元论的倾向。
刘因(1249—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河北徐水(今保定)人。征诏为右赞善大夫,未几即辞归里,具有民族意识。有《静修集》行于世。
刘因在本体论上提出太虚元气说。他在《匏瓜亭》中说:
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造物全其真,世人若其味。虽得尽天年,惜坐无用器。伊谁窍混沌,大朴分为二。②
显然,这是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思想。他认为,事物都是由太虚之气所产生,并提出天地万物产生之前气为混沌之状。他虽未肯定气是本原,但其气论实学思想倾向比上述郝经更为明显。
刘因等人朱子学气论实学思想的倾向,到了明代前期的薛瑄(1389—1464年,号敬轩,山西河津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从朱熹的笃行出发,强调气的重要性。薛瑄在论到朱熹的《四书集注》时说:
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学者当以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③薛瑄明确指出,他的代表作是按照张载的《正蒙》方式写的。他对朱熹的
理气论进行了改造,把气提到和理同样的地位,具有了初步的气论实学思想。但是,他们仍未超出朱熹的思想体系。薛瑄的思想对明代中期的罗钦顺、王廷相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王学的批判和朱学的改造,继承张载的思想传统,把朱熹思想体系中的气学倾向发展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从朱子学中分化出来。
罗钦顺(1465—1574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的气论实学思想,是明末清初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居衡山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①《朱学论丛》,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②《静修集》卷六。③《四书录》卷二。
南衡阳人)对理学进行总评判的先声。王夫之是中国气论实学的集大成者。因为王夫之的思想作为朱熹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所讨论的基本范畴大致相同而内涵相反。王夫之的思想是朱熹思想体系漫长衍变和分化过程的最后结局。在王夫之之后,朱子学尽管仍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占重要地位,但是就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史来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论实学思想已占有主导地位。
第三节 全国教育和书院
一 国学向乡校书院转化
朱熹思想流传全国后,其后学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们有的在朱熹有关的精舍、书院的基础上,或者自设精舍、书院,进行教育事业和学术活动,培养人才,撰述著作。把教育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是朱熹等书院活动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古代,教育事业是公立和私立相互补充而结合在一起的。到了朱熹活动的南宋以来,在异族和异教(主要是佛教)的侵蚀下,士风萎缩和教育经费困乏,公立教育事业更不能解决士风衰微的问题,更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于是私学有所发展。朱熹、张栻及其后学,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为中心,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教学理学,研究理学,恢复和发展儒学,排斥释道异端,振兴民族文化。他们所办的书院具有公私立学校相结合的性质。对此,韩国李朝李退溪说:
夫书院何为而设也?其不为尊贤讲道而设乎?自宋朝四书院之后,渐盛于南渡而大盛于元明之世。彼数代非无国学乡校而必更立书院者何也?国学乡校有科举法令之拘,不若书院可专于尊贤讲道之美意。故或因私立而国宠命之,或国命立之而择人教养也。若吾东方,则至当代而后始许立院,所谓因私立而国宠命者。窃仰圣朝之意,亦岂非慕数代之遗风而欲庶几,云云。①
李退溪的时代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叶。这是说南宋及其后的教育学校(国学乡校)具有公立和私立相结合的性质,并以此纠正科举法令之弊。朱熹等把书院由原来官家统制更多地转向民间私学为主导。这是其书院教育的又一大特色。
二 全国与朱熹相关的书院
在南宋元明清时代,理学家们的学院林立,形成为国家的教育网络。与朱熹有关的福建境内的书院上面已述。下面论述几处福建之外的、具有代表性的书院,以见一斑。①
白鹿洞书院 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是朱子学家进行讲学活动的重要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又名白鹿洞书堂、白鹿书院、朱晦庵书院。最初为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渤及其兄李涉隐居读书之地。传说李渤曾养一白鹿自娱,故被时人称为白鹿先生。后来,他任江州刺史,在一石洞里建造一台榭,以其别名“白鹿先生”而命名为“白鹿洞”。南唐李昇昇元四年(940年),白鹿洞正式辟为“白鹿洞国庠”,又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任洞主,执掌教授之职,并置学田授徒,学徒常数十百人。宋初改名为“白鹿洞书院”。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赐予国子监印本“九经”。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于书院故址建造学舍10余间,称“白鹿洞书堂”。不久毁于兵火。
白鹿洞书院之兴盛并扬名于天下,实赖于朱熹。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军守。当时书院已毁,朱熹疏请修复。重修后的书院,规模庞大,共有殿宇书堂360余间,其中以圣礼殿为中心,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祠、先贤祠、忠节祠等。朱熹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②,成为后来全国书院教育规章制度的范本,对后世书院体制的建设以及书院教育的推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吕祖谦撰《白鹿洞书院记》,叙其始末。始称其为四大书院之一。朱熹自任洞主,讲学其中,并邀请陆九渊等到此讲学,史称“南康之会”。陆九渊的讲题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据说听众中有人被陆九渊的讲说感动得落泪。这种讲学活动对于推动学术思想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书院毁于兵火。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重建。国子监祭酒胡俨为文记之。此后,程敏政、李梦阳等屡有修缮。胡居仁、李梦阳、王阳明等先后讲学于此。神宗万历(1573—1620年)初,张居正废书院,旋复。清代,该书院屡有修复,并被保存至今。
龙光书院 在江西丰城荣塘剑池庙左,亦作“荣光书院”。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邑人陈自俯创建①,“四方来学者三百余人”②,有六经楼、仰止堂、讲堂、戒规堂等建筑。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往潭州访张栻途经于此,在此讲学。朱熹题有《丰城荣光书院》诗③。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应丰城门人熊世基、熊世琦兄弟之请,为“其所构龙光书院之堂”撰写《龙光书院心广堂记》,其中有曰:
丰水之夏阳熊世基、世琦执经来学之明年,乾道庚寅岁(按即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也,请铭其所构龙光书院之堂。熹榜其间曰“心广”,且嘱以敷畅厥义。复之曰:“人生两间,孰无此心?”心者,贯万事,统万理,主宰万物者也。然则若之何而不广乎!克其所以为广累者,则心广矣。④
濂溪书堂 在江西九江城南濂溪巷,亦名“濂溪书院”。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建,后遭兵毁。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江州知州潘兹明、通判吕胜己重建,朱熹为之撰《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⑤是记讲了理学的基本思想,以及濂溪书堂的缘由。其中有曰:
夫天高地下,而二气五行纷纶错糅、升降往来于其间。其造化发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则仁、义、礼、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而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然气之运也,则有醇漓判合之不齐;人之禀也,则有清浊昏明之或异。是以道之所以讬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亿度而强探也。《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矣,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先生)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明其川曰“濂溪”,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按即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己,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为记。⑥
这里开头讲的理学基本思想的源流,是由《河图》、《洛书》、孔子等以至于周敦颐的,然后又由二程以至于朱熹本人。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四月六日,朱熹在知南康军任满,归家途经江州之时,曾在此讲学,“拜濂溪先生书堂遗像”,随行的有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祁真卿、昊兼善、许子春、胡莘、王朝、余隅、陈士直、黄榦、张彦先等一批弟子,以及会稽僧志南、明老等。①刘子澄请朱熹“为诸生说《太极图》义”,周敦颐之“曾孙正卿、彦卿,玄孙涛为设食于光风霁月之亭”。②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朱熹门人赵崇宪知江西江州,曾筑室26楹于濂溪书院,作为书院诸生学舍。此后,元、明、清诸代均对此有修复。
东山书院 在江西余干县冠山东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赵汝愚及从弟赵汝靓建。赵汝愚之子崇宪、崇度皆朱子门人,曾延请朱熹讲学其中,朱熹为其“云风堂”书匾。③后来,赵“汝愚卒,朱子来吊,复馆焉。后为胥吏所据,邑人李荣庭鬻产赎之。”谢枋得为记。④由此可见,朱熹到东山书院至少有两次。
怀玉书院 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金刚岭之阳。北宋杨亿曾于此建怀玉精舍。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陆九渊、汪应辰曾讲学于此,于是当政官吏和朱熹门人便在此建立书院,以供四方来学之生。⑤朱熹说:
秋冬间无事,或可出入。其思承教。……闻怀玉山水甚胜,若会于彼,道里均矣!⑥
此书写于淳熙元年(1174年)。此言朱熹与吕祖谦“怀玉之约”。但是,到了秋间,两人均因故未前往。他又约“迟至明年”、后年。朱熹说:
熹还家数日,始登庐山之顶,清旷非复入境,但过清难久居耳。至彼,与季通方议丹丘之行,忽得来教,为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至鹅湖追逐,入怀玉深山,坐数日也。损约收敛,此正区区所当从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应者,自承警诲,什损四五矣!自此向里,渐渐整治,庶几寡过,但恐密切处不似外事易谢绝也。①
朱熹“怀玉之约”终有否成行,未有明确记载。而朱熹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十一日,侍讲罢归路过玉山,县令司马迈设讲席,朱熹为诸生讲学,遗存有《玉山讲义》。朱熹到过怀玉山讲学,是肯定的。
银峰书院 在江西“德兴县市延福坊。宋淳熙间(1174—1189年)邑人余瀚、余渊延朱子讲学其中。明崇祯间(1628—1644年),裔孙应馨改建于肯堂下”。②
草堂书院 在江西玉山县北怀玉山下。据方志载:
朱子讲学于此。有青山缘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相传朱子题山下酒舍一联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旁青山不买柴。”即其地也。宋末书院废。斗山玉奕与其子介翁结庐居此。③此仅方志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处谓朱熹一联语,未见《朱子文集》,值得注意。
盛家洲书院 在江西丰城县东蓝家巷。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崇安往潭州访张栻,顺道讲学于此。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邑人盛温如在此建书院。④据方志载,有朱子《盛家洲》诗二首,其一云:
湖上阑干百尺台,台边水殿倚云开。洪桥人隔荷花语,玉碗水盘进雪来。⑤
鹅湖书院 在江西铅山县鹅湖山下,原为鹅湖寺。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人相约会讲于此,因学旨与陆氏兄弟不合而罢,史称“鹅湖之会”。对此,朱熹说:“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也。”⑥吕祖谦说:“某以五月半后,同朱丈出闽,下旬至鹅湖。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⑦朱熹有《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一首,曰: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①
后人于朱陆论辩处建四贤祠以祀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
书院前排建筑中悬有“道学之示”的御匾,四贤祠中有“顿渐同归”匾。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疏请赐额,赐曰“文宗”,故又名文宗书院。元代迁至铅山城内(今永平镇)。著名学者吴师道、程端礼等先后任山长。元末毁于兵火。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巡抚韩雍、广信知府姚堂对鹅湖寺重新修葺。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命铅山知县秦礼于旧址重建。明代宸濠之乱,书院学舍几乎毁坏殆尽。及至明末,几经重修而得以不堕。清世宗顺治十年(1653年),江西巡抚蔡士英捐资重建,并列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地方官潘士瑞曾加修葺。康熙五十四年,令尹施德大加修建。李光地记曰:
书院之建,实为国家学校相为表里。李渤高士尔,朱子犹倦倦焉。今使先贤遗址,焕然重修,江右故理学地,必有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贤者。②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亲书“穷理居敬”额。高宗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郑之桥重加修葺。编有《鹅湖讲学会编》。仁宗嘉庆十七年(1812年),吴嵩梁为山长,编撰《鹅湖书院田志》。文宗咸丰年间(1851—1861年)毁于兵火。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重建。清末改为鹅湖师范学校。
钟山书院 在江西婺源。南宋孝宗淳熙初年(约1175年),县人李缯(字参仲,号钟山)建。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初次回婺源省亲扫墓,识得李缯。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省亲扫墓,与表兄程允夫至该书院,“徜徉其间,讲论道义,谈说古今,觞咏流行”,并讲学其中。③据《语类》记载:
先生(指朱熹)游钟山书院,见书籍中有释氏书,因而揭看。先君问:“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无所得。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备具,不必它求。”④
隆冈书院 在江西南昌“府城南四十里,形如象尾相近,有澹冈及隆冈。
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8年),进士刘邦本建隆冈书院,其裔孙藏有朱子所题四景诗”。淳熙八年(1181年)四月,朱熹由南康军归闽,途次于此,作《隆冈书院四景诗》。诗分为春、夏、秋、冬四景,每景七言律诗一首。①未知此与近年在福建古田发现的朱熹《四景诗》是否相同。
双桂书院 在江西德兴。据方志载:“双桂书院在游奕坞,相传朱子赠程烨、程燧兄弟诗,有‘两种天香手自栽’之句,书院之名由此。”②朱熹此诗为《题程烨、程燧兄弟双桂书院》,原载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全诗为:“君家构屋积玉堆,两种天香手自栽。清影一帘秋澹荡,任渠艳冶斗春开。”③
据考证,此诗应为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前往婺源省墓前后所作。程烨、程燧当为朱子门人,生平缺考。“按(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二《书院》:‘蒙斋书院,朱子门人程端蒙讲学所,旧在德兴县游奕坞。’而程烨兄弟双桂书院亦在游奕坞,似程烨兄弟与程端蒙为同宗之戚,自必相识。朱熹绍兴二十年归婺源省墓,即尝经德兴拜谒名诗人董颖,德兴士子已有来执礼问学者。淳熙三年再归婺源,程端蒙又特自德兴抠衣裳来谒,程烨兄弟或亦在其时同见朱熹并请赠诗”。④
岳麓书院 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始创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创建者为潭州太守朱洞。因其址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故名。初创时,书院设有讲堂5间,斋舍52间。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对书院作了扩建,并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置田产,授徒讲学,当时学生定额约为60人。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赐《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由此形成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等基本规则。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后,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也扩大至100余人。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拜国子监主簿,并赐“岳麓书院”额。由此书院称誉天下,成为地方最高学府,位在潭州州学之上。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书院因战乱,毁坏严重,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并请著名学者张栻主持教事、讲学其间,岳麓书院遂达到鼎盛时期。宋代理学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的许多学者也曾在岳麓书院学习或讲学,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活动基地。一时之间,前来求学的士子大增。
乾道三年(1167年)秋,朱熹从福建来访张栻,并在书院会讲《中庸》,史称“朱张会讲”。据传,当时听众达几千人。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张栻去世。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因书院失修而进行修复并扩建。请醴陵贡生黎贵臣为书院执事,朱熹又将他手订的《白鹿洞学规》用作岳麓书院学规。
南宋末至明初,书院几经焚毁。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书院得以扩建,并置学田2000余亩,规模空前。嘉靖以后,王阳明门人相继讲学于此。明亡,书院亦毁于战火。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赠以御书“学达性天”额及经史诸书,因建御书楼。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御书“道南正脉”额赠之,书院得以重振。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南轩书院 在湖南衡山南岳山后,宋张栻建。张栻因父浚“奉诏居永州,栻往来省侍,受业于五峰胡宏之门,置书院于岳麓山后”①。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张栻与朱子同游,讲学于此。”②
城南书院 在湖南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建。“城南书院”门额为其父张浚手书。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与门人范念德、林用中“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③讲学之余,朱、张两人相互唱和,朱熹有《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④原诗的朱熹手迹收入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遗墨》一书中。⑤
邺侯书院 在湖南衡山烟霞峰下。唐代邺侯李泌隐居于此读书、藏书,其子蘩于南岳庙之左侧建“南岳书院”。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改称“邺侯书院”。明人重修,又改称“集贤书院”,合祀唐宋诸贤于其中。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年),复称“邺侯书院”。⑥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张栻在“岳麓会讲”之余,曾同访烟霞遗迹,并赋诗以纪。朱熹有“山道榛芜大道荒,令人瞻望邺侯堂。怀贤空自悲今昔,泪滴西风恨夕阳”的诗句。①
石鼓书院 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中州人李宽始建。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邑人李士真重建。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赐“石鼓书院”额,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②
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部使者潘畤、提刑宋若水相继修建。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应宋若水之请,为之撰写《衡州石鼓书院记》。朱熹告诫诸生不要被“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的“学校科举之意乱焉”,而要“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书院立石刻碑以传。③
姚江书院 在浙江余姚。当地有姚江,故名。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年),邑人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建于半霖,祀王阳明。邑中士有志节者,均寝食其间,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课,学阳明学,溯洙泗,逮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以申明良知之学。史孝咸主讲10年,相传“和平光霁,以名教为宗主”,由此士风大振。沈国模尝以80岁高龄,每岁自四明山至书院,为诸生讲习。黄宗羲晚年亦曾主讲于此。
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县韦钟藻移建于城南巽水门内角声苑旧址,并请著名理学家邵廷采主持讲席达17年。以讲求程朱理学为主,又竭力调和朱陆学说。钱仪吉《碑传集》详细记载了当时该书院讲会之情景。世宗雍正九年(1713年),浙江总督李卫重修。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6年),增建庑院。今有《姚江书院志略》传世。
逸平书院 在浙江江山,原名“南塘书院”。南宋高宗绍兴初年(约1132年),儒士徐存(字逸平,号诚叟,杨时门人)建,被后人称为“逸平先生与朱考亭讲学之所”。④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在中进士第后回闽途中,首次造访徐氏。朱熹在《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中曰:
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①
朱熹在《江山县学景行堂记》曰:
徐公诚叟者,受业程氏之门人,学奥行高,讲道于家,弟子自远至者,常以百数。其去今不远也。吾意大山长谷之中,隘巷穷闾之下,必有独得其传而深藏不市者,为我访而问焉。②
明方豪《逸平书院记》中谓,“吾邦有先正曰逸平先生者,徐姓,存名,诚叟其字。受业龟山,得程氏之学,与朱子实相友善,尝讲道于南塘书院。逸平既殁,朱子往吊焉。书院已为毛氏墓田,因赋诗寄哀,有‘徐子旧书址,毛公新墓田’之句。”③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知县吴仲将书院迁至城西骑石山麓,更名逸平书院。④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年),书院毁于兵火。
稽山书院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任浙东提举,在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卧龙山西岗讲学,后马天骥于此处建祠祀之。据《于越新编》所纪:
宋朱文公尝司本郡常平事,讲学敷政,以倡多士。三衢马天骥建祠祀之,其后九江吴革因请为书院。⑤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年),得以增葺。后毁。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知县张焕发重建于旧址之西麓。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阳明弟子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后为瑞泉书院。明王守仁为之记。⑥
丽泽书院 南宋吕祖谦、吕祖俭兄弟创立,在浙江金华。“丽泽”原指“两泽相连,润说之盛”,后借喻朋友之间讲习切磋。吕祖谦、吕祖俭兄弟晚年创设丽泽书院,讲学会友。吕祖谦常邀请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讲学。吕祖谦编著《近思录》(与朱熹合编)等,供学徒学习。还手订《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①据传,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该书院,在当时的教育界及思想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吕祖谦在该书院所讲内容,由其弟祖俭等人编为《丽泽讲义》。
吕祖谦死后,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吕氏门人请修书院,官府允之。建吕祖谦祀室及遗书阁,并开始刊刻图书。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吕氏门人又将吕祖谦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以吕祖俭配祀。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知州许应龙迁书院于双溪之畔,奏请理宗御赐匾额。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又迁至旌孝门外印光寺故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后任山长、主讲,四方来学者甚众。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又有重修之举。后毁于明末。
清全祖望说,“明招学者,自成公(祖谦)下世,忠公(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岳麓书院)之泽,并称克世……而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②说明该书院在培养人才、保存古代文献等方面有诸多贡献。
樊川书院 在浙江黄岩杜家村。《赤城新志》载:“晦庵先生与南湖二杜公讲学之地。”南宗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任浙东提举时,巡历至台州,曾至黄岩。“在县北六潭山,朱文公尝著书其麓,名为小樊川,题曰溪山第一”。③黄岩的朱子门人有杜贯道、杜煜、杜知仁、池从周等,后杜知仁侄孙杜范建“紫阳书院”,后有朱文公祠。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知县刘宽更名为樊川书院。
文献书院 在浙江黄岩委羽山。《赤城新志》曰:
元枢密副使刘本仁建。以朱文公尝施教于台(州),杜清献公得其传,因祀文公于此,而以清献配焉。危素、朱右俱有记。④
杜清献即杜范,字成之,朱子门人杜煜、杜知仁从孙。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官至右丞相。《宋史》杜范本传谓其“少从其从祖烨(煜)、知仁游,从祖受学朱熹,至范益著。”⑤可见杜范本人并未直接从学于朱熹。后人以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官浙东提举时,曾巡历台州,讲学黄岩,而杜范又是其再传弟子,故建此书院以祀。
龙津书院 在浙江奉化,原名“龙津馆”。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泊舟于此,率诸生讲学焉”。①理宗景定初年(1260—1264年),立龙津书院于此。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改名“文公书院”。“知州李炳移建于州之宝鹿山,山长任士林为记”。②
紫阳精舍 在浙江诸暨旧县署侧。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官浙东提举时,曾延当地名士杨文修“谈名理及医学天文地理之书,数日去”。“紫阳精舍,一名义安精舍,在旧县暑例。宋朱子为常平使者,召杨文修与谈理学,因此宿焉”。③后人因建精舍以祀之。
泳泽书院 在浙江上虞,元世祖至元年间(1279—1294年)创于西溪湖滨,方枢密移于金壘山东。因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曾讲学于此而立祠祀之。④
明善书院 在浙江松阳西20里。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为“修举赈荒事”至松阳。时邑人叶震“隐居教授于家塾,执所业见焉。朱子与语而有契,为讲《论语》、《孟子》”。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其后人叶再遇即其家塾而扩充之,称明善书院,以祀朱熹。⑤
独峰书院 在浙江处州缙云仙都山。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朱熹任浙东提举时,因连续上疏弹劾唐仲友,未报,“二十二日入处州缙云县界讫,累日以来,恭候威命,未有所闻”。⑥于是,到缙云县东仙都,“徜徉于此山,以伺朝旨,有‘于此藏修为宜’之语”。“爱其山水似武夷”。⑦在游历唐代诗人徐凝故居时,作《追和徐氏山居韵》绝句一首。诗云:
山岫孤云意自闲,不妨王事似连环。解鞍磐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山。⑧
并曾在此讲学。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邑人叶嗣昌于仙都山独峰前建此书院以祀朱熹。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邑人潜说友即旧址扩而新之。
美化书院 在浙江缙云东美化乡。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时,曾在此讲学。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年),知县陈大猷、县尉陈实因建书院以祀之。①
五云书院 在浙江缙云五云山下。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6年),楼如浚建。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知县方润重建。因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曾到仙都讲学,邑人曾建独峰、美化两书院祀之,但年久均废,因立此书院继祀。②
鄮山书院 在浙江宁波府城西五里,元邑人赵儒(应为赵寿)建,设山长主之。袁桷为记。“元大德三年(1299年),乡儒赵寿建为祠,以祀朱子,久圮。”③
朱熹生前有否经履宁波,未有明确记载。但是,朱熹曾在浙东任职,不能排除其未到过宁波。赵寿建此书院,起因乃其祖赵善待(字时举)曾从朱熹学。④
包山书院 在浙江开化北。南宋孝宗乾道末年(约1173年),邑人汪观园、汪杞兄弟建“逍遥堂”,又名“听雨轩”,以课读子弟。汪观国二子汪湜、汪泓均从吕祖谦学。
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朱熹回江西婺源省亲,曾与吕祖谦相约于此,论辩讲学数日,两人讲论的课题涉及《毛诗序》、《易》、《春秋》等。朱熹有《汪端斋听雨轩》七律一首:
试问池堂春草梦,何如风雨对床诗。三薰三沐事斯语,难弟难兄此一时。为母静弹琴几曲,遣杯同举酒千卮。苏公感寓多游宦,岂不临风尚尔思。⑤
听雨轩因朱、吕讲学而闻名,汪观国之子汪泓“立书院以祀朱、吕二先生,后孙继荣请于朝”。⑥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御赐“包山书院”匾额。
五峰书院 在浙江永康方岩寿山坑。因寿山坑有鸡鸣、覆釜、瀑布、固厚五峰而得名。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吕祖谦、陈亮等曾在固厚峰下石洞中读书讲学,时称“三贤”。堂侧摩崖上,有陈亮手书“陈龙川、朱晦翁、吕子约尝同游”,有朱熹手书“兜率台”石刻。①
明世宗嘉靖初年(约1523年),“邑人应典因为祠以祀三贤,知县洪垣更为书院”。②
石洞书院 在浙江东阳。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邑人郭钦止(德谊)建。其子津、浩均为朱子门人。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二月,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曾到此讲学,赠送所著《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后郭津曾将书院重修,并请朱熹为之撰记题匾。朱熹说:
书院规模,且随事随力为之,却就事实上考察整理,方见次第,不须如此预先安排。记文匾膀,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见浮浅外驰之验。若于学问全体上切己处用得功夫,即气象自当深厚宏阔矣。③
朱熹虽不曾为此书院撰记,但却题写了“洞山”、“月峡”、“流觞”刻于石壁之上,并为书院创建者郭德谊书写《郭德谊墓志铭》④。叶适有《石洞书院记》。⑤
月林书院 在浙江上虞,宋潘畤建。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官浙东提举时,潘氏曾延朱熹在此相与讲明性命之学。从学者有潘畤之子潘友文、潘友端、潘友恭及孙邦仁等。⑥后朱熹离任,曾举潘友恭以自代。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潘畤逝世,朱熹撰文祭祀。⑦
月泉书院 在浙江浦江西北二里。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浚泉建亭,名为泉亭。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正月,朱熹以浙东提举巡历过浦江,曾讲学于此。朱熹说:“(臣)于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县界,历义乌、金华、武义县。”⑧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知县王霖龙建“月泉书堂”,亦名“月泉精舍”。据记载:
以是州东莱先生吕成公讲道丽泽、紫阳先生朱文公尝提举浙东常平,行部过此,且与成公友善,遂于此地阐明正学。乃祠二先生于月泉精舍,
使学者瞻仰兴慕,肄业其中。①
元代升为书院,置山长。元明两代,历经重修。
瀛山书院 在浙江淳安北40里银峰之麓,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邑人詹安于此建双桂书堂,收詹氏弟子入学。其孙詹仪之,乃朱熹门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其后人詹骙中状元,故取“登瀛”之意,改书堂名为瀛山书院。据方志载:
瀛山书院,在县治北四十里。……宋熙宁间邑人詹安辟,其孙仪之与朱子论学于此,朱子有“半亩方塘一鉴开”之句。明隆庆三年,知县周恪访名贤遗迹重建,王畿为记。②
今学者据方志、淳安《詹氏宗谱》、明王畿《瀛山书院记》以及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南州后学闵鉴所书方塘诗石碑,著文论证方塘在淳安瀛山③;或言朱熹生前曾分别于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乾道九年(1173年)、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三次到瀛山书院讲学。④对此,束景南考证说:
《朱文公文集》卷二及卷三十九《答许顺之》书十,均有此诗而无此题(按指《方塘诗》),“惟有源头活水来”均作“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名《观书有感》非访詹虚舟仪之有感而作,宗谱、书院记均不可信。遍考朱熹生平仕历游踪,断无往淳安游访之可能,石碑诗题之伪不待一辨。……后世各地据朱熹此诗附会“方塘”并构“天光云影亭”甚多,以予只就方志所见,不下五六处,淳安瀛山不过附会之一也。⑤
考《朱子文集》,朱熹与詹仪之的书信凡五通,未明确讲其到淳安讲学。⑥
宗晦书院 在浙江乐清县治东。宋建,以祀朱熹。旧名艺堂书院,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改名宗晦,取宗晦庵之义。方志载:“宗晦书院,在(乐清)县治东。宋杨艺堂立,有文公祠,故名。”⑦
南山书院 在浙江宁波,为宋代沈焕(1139—1191年,谥号端宪)讲学处,宋理宗赐额。朱熹与沈焕谈道住宿于此。时比白鹿洞书院。①朱熹与沈焕的关系,朱熹说:
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杨敬仲、吕子约,所闻者沈国正(焕)、袁和叔(燮),到彼皆可从游也。②
“所识”乃指见面相识,“所闻”则未尝见面。陈来考定此书约写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滕璘官鄞县尉赴任之际③,时已是朱熹官浙东提举之后,而此后朱熹再也未曾到过浙东。因此,上引所谓“谈道住宿”于南山书院是有问题的,应该进一步研究。
东屿书院 在浙江台州温岭。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邑人丁少云建。有松山、南麓诸亭池、楼阁及“东屿书房”。少云子、进士、青田县令丁木又建云海观、台榭岩径等70余所,为浙东冠。④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应丁木之请,作《题东屿书院》五言八句一首。诗曰:
书房在东屿,编简乱抽寻。曙色千山晓,寒灯午夜深。江湖勤会面,
坐卧独观心。秋浦瓜期近,何当寄此吟。⑤
石门书院 在浙江青田石门洞。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提举浙东,循行至此,有汶上之兴。元惠宗至正年间(1279—1294年),廉访使王俣始即谢客堂故址建。“汶上之兴”令人不知所云。考清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有《训蒙绝句》百首,其中第四十五首题为《汶上》。故所谓“汶上之兴”,殆指朱熹循行至此,触发了诗兴,留下了绝句一首。诗云:
仕非其地宁无仕,此地还他德行人。彼以势邀吾自逝,丈夫无欲气常伸。⑥
从诗意看,比较符合朱熹在浙东任上因连续弹劾唐仲友而未能奏效的激愤心情。
据方志载:“石门书院,在县西七十里石门洞。《续文献通考》:宋淳熙九年,朱文公提举常平至此,欲居之。元至正中廉访副使王俣始即谢客堂故址建,不久圮。”①所载与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大同小异。因朱熹有《汶上》诗,此书院可列入因朱熹题诗后所建之书院。
紫阳书院 在徽州城(今安徽歙县)南门外,宋理宗亲笔题额。徽州城南五里有紫阳山,朱熹父朱松少尝在此山读书,及至入闽之后亦常思念此山,曾刻以“紫阳书堂”作为自己的印章。后来,朱熹寄寓福建崇安五夫里时,曾“牍所居之厅事堂曰‘紫阳书堂’”②。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两次回婺源扫墓祭祖。“其时,思返旧庐,滞留数月,执弟子礼者三十人”③。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朱子门人赵师端为徽州知府,立朱文公祠堂于郡学,黄榦为之记。④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因郡守韩补之请,于城南门外建为书院,宋理宗赐额“紫阳书院”,教授诸葛泰为记。书院依山傍水,前为书楼,后为宸奎阁,其规模宏大、壮观。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又加以重建,方回为之记。⑤
一 由闽中而全国
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闽学)是闽中之学,是与濂、洛、关等之学相并称的地域性的理学学派。但是,由于它在创立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被统治者所认识,很快由初期活动的闽、浙、赣地区而全国,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前面讲到,朱熹在世时福建朱子学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数百名朱熹门人分别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在“庆元党禁”时期和朱熹死后,他们大都返回原籍,在全国各地传播朱子学。清人黄百家在论到朱熹浙江崇德籍门人辅广传播朱子学的情况时说:
所传之学,蜀则有魏鹤山了翁;闽则有熊勿轩禾、陈石堂普;吾东浙,
自韩恂斋翼甫传子庄节性、余端臣,再传而有黄文洁震。①这就是说,辅广通过四川的魏了翁、浙江的韩翼甫及其子韩性、余端臣、黄震,把朱子学传至四川、浙江。对于魏了翁,据记载:
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②
李燔是江西永修籍朱熹门人。李燔除把朱子学传给魏了翁外,还亲自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传播朱子学。据记载:
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按即今湖南岳阳),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禀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改襄阳府(按今属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属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①
非福建籍的朱熹门人大都像辅广、李燔这样在各地传播朱子学,从而朱子学流传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朱子学系,如江西系、浙江系等。
在朱熹门人传播朱子学的过程中,福建籍朱熹门人黄榦居首要地位。他以得朱熹遗命自任,以墨子辟杨墨自励,呼喊着“卫道岂可以不严乎”。他曾讲学于江西庐山白鹿书院,“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邦寺以处之”。②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③
此叙朱子学由宋而元,路线分明。全国各地初传之朱子学,大多出于黄榦之门。黄榦曾知江西临川。浙江金华人何基之父为临川主簿,命何基师事黄榦。黄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悚惕受命”。金华人王柏闻何基从学黄榦得朱子学之正传,乃往学于何基,何基告以“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④金华金履祥从学王柏、何基,得朱子学真传。金华人许谦又受学于金履祥。此所谓“金华四先生”皆出黄榦之门,“推源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⑤朱子学盛行于浙江,实黄榦之力也。
黄榦为江西新淦县令时,其地饶鲁(号双峰)从其学。因此,“双峰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①全祖望说:
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子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按程若庸),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合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终近乎朱。②
这就是元代江西朱子学之源流,亦是以黄榦为纽带。
朱子学流传于北方,与黄榦曾知德安(今湖北汉阳)有关。窦默避元兵逃至德安,县令以程朱性理之书予之,可知黄榦把朱子学传至德安。③后来,元兵入侵德安。杨维中为大将军,其幕僚有姚枢从俘虏中求儒者数十人,其中有赵复等人,带自燕京(今北京),建太极书院,由赵复等人讲学,授程朱所著与其诸经传注,门徒数百人。此亦知赵复等人之学亦是在德安由黄榦所传。朱子学传之北方自此始。姚枢在北方刊朱熹《论孟或问》、《小学》等书。其后,姚枢居辉县(今属河南)苏门,河南沁阳许衡至,尽录程朱传注以归。上述杨惟中、窦默、姚枢、赵复、许衡等,皆是元初名儒。可见,北方朱子学之传播,亦渊源于黄榦。
对于朱熹门人和再传门人传播福建朱子学和福建朱子学流传的情况,清人蒋垣有概括的叙述。他说:
朱门受业为多,最知名者黄榦、李燔、张治、陈淳、李方子、黄颢、蔡沉、辅广等。而黄榦门人最多,潘柄、杨复、陈宏、何基、饶鲁皆其高弟。基传之王柏,柏传之金履祥,履祥传之许谦,饶鲁传之吴中行,中行传之朱公迁。时与朱熹同任道学者吕祖谦、张栻。祖谦受业于侯官林之奇。当时杨、胡、林、朱、黄、蔡之学盛行于江之东南。张拭,成都锦竹人。至宗、宁间,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辅广、李燔之学授教生徒,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则闽学传之西蜀矣!理宗时,杨惟中建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又姚枢隐居苏门,以道学自任,刊《小学》、“四书”,及蔡氏《书传》、胡氏《春秋传》,而闽学至于河溯矣!此八闽道学(理学)源流之大概也。④
河溯(朔),泛指黄河以北。《书·泰誓中》有“王次于河朔”之语,孔传谓“渡(黄)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由此可见,闽学传播至全国。清人张伯行在《道南源委·序》中说: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子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①
到了明清时代,福建朱子学学者还致力于把闽学往外省传播。例如,清初福建人龚景瀚在关中、李光地在河北河南、蔡世远在江浙、蓝鼎元在广东台湾、阮旻锡在山东、林嗣环在海南岛、黄志璋在广西两湖、林之浚在云南贵州、朱兆纲在山西安徽、吴鸿锡在四川等,传播朱子学。
据以上诸家论述,朱子学由闽中而全国的大概情况如下:
二 国家的正宗思想
随着朱子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全国传播,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它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早在朱熹死后的第二年(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十月,宁宗皇帝就下诏赐谥,除朱熹“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②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十月,诏赐谥朱熹曰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理宗皇帝在封制中谓,朱熹遗著“有补于治道”。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理宗皇帝谓,“深有不同时之恨。每阅‘四书’之奥旨,允为庶政之良矩”。①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宗皇帝诏学宫列朱子从祀庙堂。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复科举,诏定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诏建朱子祠,“立徽国文公之庙”。②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皇帝命礼部传谕规定: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需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③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朱熹、真德秀等福建朱子学学者的经典注疏。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康熙皇帝先后谕敕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编辑《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由上可见,在南宋末和元、明、清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成为法定的教科书,是学者必读的课本,文官考试不出朱子学界限。朱子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正宗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在朱子学控制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七八百年中,其渗透到思想意识的各个领域之中。近代著名的福建籍学者严复说:“吾侪今日(按19世纪末)思想、风俗、政治,直接间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④“籀”即归纳推理。意思是说,宋元明时代的思想意识都渊源于程朱理学,而集理学之大成的朱子学(闽学)即发源于福建。
第二节 全国的派别和衍变
一 衍变的内在倾向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差不多又经过了三四十年,至元仁宗时(1312—1320年)就遍及全国。朱子学在福建的传衍和分化是个雏型,全国朱子学的派别和衍变是其在福建传衍和分化的扩大和发展。
由于朱熹综罗百代、集诸儒学之大成,非某个后继者所能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集大成,体系庞大,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对全国朱子学衍变的内在倾向,今人蒙培元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说:
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个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论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①
蒙培元对南宋末、元、明时代哪个朱子学家属于哪一哲学倾向,以及按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其这里的概括说明是很确切的,为研究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提供了指导性线索。
朱子学超出闽、浙、赣范围成为整个国家的正宗思想后,它根据理论自身的规律和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进行衍化。基于上述黄榦是朱子学由闽至全国的桥梁,朱子学在全国的衍化是在黄榦思想中开其端的。黄榦固守师说,只是在体之用上有所阐发。南宋末黄震曰:
晦庵论近思先太极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能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耳。②
这里黄震叙述了黄榦思想与朱熹思想之不同,在黄榦思想中就埋下朱子学日后分化的根苗。体用关系体现为理一分殊,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人的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孟子的四端说来说明道德的体用关系。黄榦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③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道德之体,有此体必然表现为与此体相联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道德之实践(用);抽象的天理世俗化,为人人得以遵循的道德准则,通过格物明理实现人内心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道德之善;实际上,格物明理和明内心的道德之善是对立的。这是黄榦哲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
朱子学于元初盛行于全国之后,其衍化大致有三派:一是以赵复、许衡为代表的北方一派,一是以何基、许谦为代表的浙江金华北山学派,一是以饶鲁、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广汉双峰学派。这三派大致按上述黄榦思想中的三种倾向进行衍变和分化,走向不同的学术道路,因而使朱子学原来理论上的裂痕走向解体的道路。
朱熹思想的解体和分化促使朱子学的演进,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本身的发展必然会解体和分化,同时其庞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其后一二个后继者所能继承和发展的。南宋至明朝末年,朱熹思想向两个方向分化和发展: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两种方向发展的结果。最后出现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陈献章、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和以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学,都是从朱熹思想体系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由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中国社会由古代孕育着近代。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朱熹,其内圣成德达到了成熟和综合点,其后以此为新的起点往前发展,即向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的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时期,西方社会也正开始近代化,出现“文艺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是与西方同步的,或者说早于西方。牟宗三在讲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时,深刻指出:
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300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民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200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向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两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
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①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就是他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理想往前发展,推翻清王朝,开出一个外王事功的大时代,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
二 黄震 金华四先生
南宋末年浙江朱子学有辅广系黄震、黄榦系金华四先生等。对此,《宋元学案》有所综合评述。其曰:
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平生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即江西)诸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子(金华四先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折衷诸儒,即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②
浙江的朱子学,对朱熹的思想,黄震有较大的修正,金华四先生则是墨守朱熹家法,因此分开论述。
黄震(约1213—1280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浙江慈溪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历官吴县、华亭县、长洲县尉,史馆校阅,广协、绍兴通判,抚州知府,江西、浙东提举常平等。宋亡后,“日惟一食,仰天长恨,祈速死”,最终“饿于宝幢而卒”③。其著作有《黄氏日抄》(即《慈湖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仰天遗草》等。
黄震对天理的论述,基本上与朱熹同。而在讲到理与道的关系时却对朱熹有所修正。如黄震说:
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④
黄震强调,道不在天地人事之外。这跟朱熹的讲法是有所不同的。朱熹认为,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理,是人道;作为万物本原的理,是天道,而天之道则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外的。这就对朱熹之“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所修正。由此,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之“道不必贯而本一”的观点。他说:
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说也,而可以乱圣言哉!①
他认为,朱熹后学“舍孝弟忠信不讲而独讲一贯”②的倾向,是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论的断章取义,是道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点。
黄震认为,朱熹等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是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不一致的。他说:
人生而有性,已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与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虚空中别可言性,则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说也。③
他认为,“性相近”包括了气质和天地之性,而不是朱熹等所说的只是“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哪里有三品来?”④在朱熹看来,韩愈的性三品是指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没有三品的问题。对此,黄震说:
性有三品之说,正从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来,于理无毫发之背。至伊、洛添气质之说,又较精微。盖风气日开,议论日精,得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对说,而后孟子专指性善之说举以属之天地之性,其说方使无偏。此于孟子之说有功而于孔子之说无伤。实则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言。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说本于上智、下愚之说,而后进喜闻伊、洛近日之说,或至攻诋昌黎耶?⑤
在黄震看来,韩愈之性三品说,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二程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致的,而朱熹却说性三品不包括天地之性,不是相矛盾吗?
在知行问题上,黄震强调躬行。他说:
自晦翁之学盛行,而义理之说大明。天下虽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随之而渐生。盖论说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曾用力于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说?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见言晦翁之学者几人,往往不知其躬行。
……世所谓《中庸》、《大学》者,身未必行,惟见笔舍华靡。①
在这里,黄震批评了朱熹后学“笔舌华靡”的空谈义理、不知躬行的行为。
由上可见,黄震对朱熹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有所立异的。因此,黄震在朱子学发展史上,不仅有继承,也是有所发展的,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
金华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9年,字子恭,学者称北山先生)及其弟子王柏(1192—1274年,字会之,号鲁斋)、柏弟子金履祥(1232—1303年,又名祥、开祥,字吉父,号次农,因家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祥弟子许谦(1270—1337年,字益子,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生),是朱子学浙江金华之主要传人,被朝廷列为朱子学的正宗。《宋元学案》专立《北山四先生学案》,详述其朱子学思想。
北山学派的何基等人,严守朱子学门户,强调读书传览为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何基语录》说:
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②
他们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寸步不离,确守师说。清初黄宗羲说: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③
北山学派由确守师说,只注重读书穷理,继承和发挥朱子学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虽然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但是由于走向章句训诂的道路,使朱子学变成烦琐哲学,没有开辟出新的境界。特别是其中的王柏,他的《诗疑》、《书疑》,原是对朱熹《诗集传》的继承,却走向极端,偏离了儒学正统,受到后世朱子学者的批评。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更觉朱子学正统派的空言无实。清代前期,虽有福建朱子学学者李光地及其他理学名臣大倡朱子学,使其一时兴盛;清末有朱次琦(1807—1881年,广东南海人)、杨昌济(1871—1920年,湖南长沙人)、辜鸿铭(1897—1928年,福建厦门人)等人提出重整朱子学,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和朱次琦同时的文廷式(光绪帝珍妃的老师)曾谓朱熹“训门人语多痛切,数十世后如见其人”。①朱次琦提出“朱子百世之师”,朱子“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②
杨昌济曾先后留学日、英、德等国9年。他在五四运动前期的中西哲学论争中,采取调和折衷态度,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实际上他立足于程朱理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讲授伦理学。他说:
所谓不限于西洋之理论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③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学应为体(正宗),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应尊为儒家思想的典范。他为讲授伦理学而编写的《论语类钞》共38条,其中有朱熹语录释《论语》者达22条,占三分之二。如第22条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首先就引用了朱熹一大段语录,即: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道,譬则天地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就是说,太极(道之体、一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万殊各得其所”就是太极(道之体、一本)的体现或作用。这段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典型表述,杨昌济解释说:
宇宙为一全体(即一本、太极),宇宙间所有一切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同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
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熹下列一段话,其曰:“吾子之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有见者也。”⑤杨昌济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来论证如何积累知识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此外,杨昌济还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吸取和发扬朱子学。
由上可见,直到清末和民初,朱子学正统派在一些学者中和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就全国来说,朱子学终未能真正恢复其元气,在理论上未有多大进展,而且趋于终结,这就是由自我窒息而后日趋沉寂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三 双峰学派 饶鲁 吴澄
《宋元学案》谓,黄榦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江右即江西,其代表者为双峰学派之饶鲁、吴澄等。“双峰(饶鲁)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吴澄)”,其学术活动时期为宋末元初。
饶鲁(生卒不详),字伯舆、仲元,号双峰,江西余干人。据载,“庚申(1206年),诏饶州布衣饶鲁,不事科举,一意经学,补迪功郎、饶州教授”①。其著作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学庸纂述》、《西铭录》、《近思录注》等。
对于饶鲁之朱子学,有谓不拘于章句,一如朱子之于二程,“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②。可知饶鲁不是墨守朱熹门户的。饶鲁认为,理气不相离,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气为理之衬贴。他说:
“浩然之气”,全靠道义在这里面做骨子。无这道义,气便软弱。盖缘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理是气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气。以有太极在底面做主,所以它底凭地浩然。③
这里全是朱熹之理气关系的说法。他又说:
“发育万物”,以道之功用而言,万物发生长育于阴阳五行之气,道即阴阳五行之理。是气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极于天”,以道之体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无过于天者。天之所以为天,虽不过阴阳五行浑沦磅礴之气。而有是气,必具是理。是气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全体大用,极于至大而无外有如此者。④
此是说理气相即不二。这里还讲了道的体用关系,即其所谓“道之体段”、“道之功用”。道是弥沦天地的,是主宰天地之气的。
饶鲁继而认为人道的极则是天理。他从性为人所禀之天理出发,发挥了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观点。他在疏解张载的《西铭》时说:
《西铭》一书,规模宏大而条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尽。然其大旨,不过中分为两节。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后一节言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何谓人为天地之子?盖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是性,犹子受父母之气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举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为大父母。故以人而观天地,常漠然与己如不相关。人与天地既漠然如不相关,则其所存所发宜乎?①
由此,他得出:“言天以至健而始万物,则父之道也;地以至顺而成万物,则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间,禀天地之气以为形,而怀天地之理以为性,岂非学之道乎?”他把天人地释为父子母,是有新意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生,是天地之气以为形,天地之理以为性,故天地与人,犹如父母之与子。因而天地与我一体,即他所说的“物吾党与”。
饶鲁进一步指出,人本身具有善端,人都有自新的欲望,即所谓民之心本自好善而恶恶,熟不欲自新?因为,仁即心,心之存即是识仁而成仁心。他说:
诚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颜子问仁,夫子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紧要在四个“勿”字上。仁属心,视、听、言、动属身,“勿”与“不勿”属意。若能“勿”时,则身之视、听、言、动便合礼,而心之仁则存,以此见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在意之诚不诚。所以,《中庸》、《孟子》只说“诚身”便贯了。②
这里的说法与朱熹之心统性情说不同。在朱熹那里,人禀受天道为性,故性具天理;心不等于性,故心不等于天理。而饶鲁却认为,心即仁,故仁同于天理。这同陆九渊的“心即理”相似。在饶鲁看来,心之能存与否,全在身之视、听、言、动,而视、听、言、动又在于“意之诚不诚”,故“诚”就将诚意、正心、修身三事贯串起来。诚即无妄、不自欺意。
饶鲁提出以敬为诚的存养省察工夫。由此他喜欢静坐。他说:静坐时,须心主于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言于敬,亦静坐不得。心是个活的物,若无所用,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圣人说“难矣哉”,意甚该涵。③
他认为,通过静坐,就能收敛“野马”之心,使本来的善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禅家的“修心”、“守心”相类似。
上面讲的居敬,只是饶鲁为学之一。他认为,为学四方,即立志、居敬、穷理、反省。①他的为学之方由“立志”始,然后居敬、穷理,而终止于反身。这是内外结合的方法,是符合理学家的“涵养须用敬,进德在致知”的原则的。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历官元朝之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制诰、集贤殿直学士等。著有《五经纂言》、《皇极经世续书》、《道统图》等,清人辑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文正公外集》。
在元代,吴澄与许衡为名儒。许是北方人,于元初“粗迹”朱子学。吴是南方人,直承朱子学大家,是“正学真传”。因此,元代朱子学有“南吴北许”之称。
吴澄以朱熹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其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享,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②
这段话值得注意者,一是韩愈论道始于尧舜,而吴澄则据董仲舒意谓道始于天,此说出了宋明儒的本体论。二是其用《周易》之元、亨、利、贞把历史顺序规定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每一段又分元、亨、利、贞。三是他把朱熹说成是“利”,而不是终结“贞”,一方面他不把朱熹看成为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似乎把自己看成是“贞”的地位,以跻身宋儒诸子的继承者之列。所以,上引《元史》本传接着谓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吴澄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是对朱熹的经学有较大的补充和发挥。他的《五经纂言》,实际上完成了朱熹的未竟之业。朱熹曾与吕祖谦等商议编次“三礼”,而终老未及为。朱熹曾说:
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于本经之下。③
但是,朱熹只留下草创本《仪礼经传通解》。后来,黄榦等也曾治礼,没有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吴澄从中年到晚年,几乎倾一生精力,完成《五经纂言》,实现了朱熹的未竟之业。他在《诸经序说》中说:
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仪礼)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稿,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夫以《易》、《诗》、《书》、《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其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①
吴澄“辄因”朱熹筹画之意,以《仪礼》十七篇为经,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例,将《礼记》(大小戴记和郑注)分类编次,纂成《仪礼逸经》八篇。就是把《礼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礼记》中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此二篇并与《小戴礼记》相参校),又把郑玄《三礼注》中的《中霤》、《禘于太庙》、《五居明堂》,共成二卷八篇。另外,又将大、小戴记中的《冠仪》、《昏仪》等八篇,和《礼记》中的《乡射仪》、《大射仪》二篇,辑成《仪礼传》十篇。这样,吴澄把汉以来流传的《礼记》(大小戴记,以至郑玄《三礼注》等)肢解,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这不仅完成了朱熹生前的夙愿,而且经过这样的整理,使流传千百年来“难读”的一部《仪礼》,得见崖略,诚是经学史上的一大贡献。②
吴澄治五经不守朱子学门户。如其《易纂言》,自称“用功至久,皆自得于心,有功于世为最大”③。在这部《易》学中,就有和会朱陆的地方。
在本体论上,吴澄认为太极即道。他说:
所谓极也,道也者,无形无象,无可执著。虽称曰极,而无所谓极也;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④
“太极”所以能起主宰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含有动静之理,它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如人之乘马,人随马的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它“常常如此,始终一般,无增无减,无分无合”。所以太极尽管包含动静之理,而主宰世界的生成、变化,它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⑤
吴澄进一步把太极说成是理、天理,而把理、天理释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者。他说:
气之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气之往来屈伸而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命各虽殊,其实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①
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②
太极与理的关系,就宇宙本原来说是太极,就宇宙化生二气五行以至万物的过程来说是理。这样,理就是万物所以形成的理,而太极就是理的全体。万物中具体的理与本原的太极是万理一原的关系。所以,整个世界由它的本原到化生万事万物的现象界,都是由于太极和理的一系列的作用。
吴澄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太极,是人道的极则,也就是天理。那么,人是如何去认识它呢?是从吾心去体认,还是从万物去参究呢?是立之于本心,还是格之于外物呢?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在朱、陆之后,吴澄则是“和会”两家之说,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方法。
在吴澄看来,湛然纯善的天地之性附于人的时候,随着各人气质的清浊不同,而有善恶之分,因而有了气质之性。但是,即使是那些因气浊而恶的人,其天地之性亦在“其中”,只是“拘碍沦染”于浊气而已。悬之于高远的天地之性,不仅予性善的人,而且也予性恶的人。这就给具有气质之性的那些恶与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他说:
人之明德,即天所以与我之明命也,自天所赋于人而言而谓之命,自人所得于天而言则谓之德,其实则一而已。然常人为气禀物欲之所昏,而不察乎此,是以昏昧蔽塞不能自明,至于梏其性而忘之也。故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所以与我之明德而有察焉,则必然因其所发,而致其学问思辨推究之功,又能因其所明,而致其存养省察推行之实,则吾之明德,亦得以充其本体之全,以无气质物欲之累,而能明其大德与尧无异矣。③
在吴澄看来,“明其德”不是由身外格物以明理,而是求之于己,自明其心。故他自己概括其方法为“自新”。可见,他主张自省自思而达到自觉,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相违背的,而与心学派明心穷理却是接近的。
吴澄认为,自省自思而自觉即是诚与敬。他说:“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敬为之主。……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①他又说:
凡所应接,皆当主于一心,主于一,则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处自无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积久,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②黄直卿(榦)谓敬字之义,近于畏者,最切于己。凡一念之发,一事之动,必思之曰:此天理抑与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则不敢为,惴惴儆慎,无或有慢忽之心,其为之敬也。③
吴澄所谓敬,就是在“一念之发,一事之动”时皆以天理来约束思维;凡一念一事,都要想一想这是天理还是人欲。他完全排除了外物之诱惑。先秦思孟学派提出“诚者天之道”,是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人道的极则。人能“思诚”即可达于“天之道”的诚。④吴澄所谓“思诚”,就是思我心中固有的诚。他说:
人之初生,已知爱其亲,此实心自幼而有者,所谓诚也。爱亲,仁也。充之而为义、为礼、为智,皆诚也,而仁之实足以该之。然幼而有是实心,长而不能行,何也?夫诚也者,与生俱生,无时不然也,其弗能有者,弗思焉尔。五官之主曰思……所以复其真实固有之诚也。⑤
他把诚说成是与生俱来,自幼而有。诚的内容就是爱其亲,也就是仁,它充实显露之后就是义、礼、智。在吴澄看来,它是具体的,并非是悬之于心外的一种神秘境界。而要保持自幼而有的诚,就是思。所谓思,就是去其恶欲和复性的冥悟过程。这样,就是去掉“人欲”,以达到所谓真实“不妄”、“不自欺”。由此进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的道德之善走过来的,反对单纯读书明理,强调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双峰语录》有说:
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⑥
在饶鲁看来,道理须是涵养,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来?可见,双峰学派是沿着黄榦的明内心道德之善的思路上往前衍变的,其心学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吴澄的心学思想更加明显。韩国李朝李退溪在讲到吴澄时曰:
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公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①
吴澄对朱熹和陆九渊两家都很推崇,他在《与许左丞书》中认为,“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②。全祖望谓吴澄“固朱学”、“兼主陆学”。③
到了明代,先有吴与弼(1391—1469年,号康斋,江西崇仁人)提出“敬义夹持,明诚两进”④,发明代心学之端;再经陈献章(1428—1500年,号白沙,广东新会白沙里人)而至王阳明,把朱子学衍变为心学。王阳明是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者,即心学从朱子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并与朱子学相对立。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阳明学是理学由烦琐变为简易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启蒙思想的出现而要求冲破朱子学一统天下的结果。阳明学差不多盛行了一百年,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正统派朱子学抬头和王夫之等人战斗的气论实学的出现,王学即告终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 北方学派 许衡
元初朱子学传入北方后,很快就形成为以赵复、许衡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李退溪在讲到赵复时说:
姚公(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公(按指赵复)传其学。由是许公衡、郝公
经、刘公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公始。⑤当时属于北方朱子学派的还有窦默等人。全祖望谓“河北之学传至江汉(赵复)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⑥
这里主要论述许衡。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等。他为元朝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即运用朱子学治国,其朱子学思想被称为道统正脉。他在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期间,向蒙古弟子传播朱子学,使当时学人皆诵习程朱之学,有“以夏变夷”之功。卒赐荣禄大夫,谥文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祀孔庙。
许衡的著作有《大学要略》、《大学直讲》、《稽古千文》等,后辑为《鲁斋遗书》。近年台湾中文出版社据日本宪文九年(1669年)刻本影印出版《鲁斋全书》。
许衡为学,一以朱熹之言为归。实际上,他主要发扬朱熹的心学思想,把朱子学变成以“尊德性”为主的践履之学。他认为,朱熹的著述太多,重点不突出。“许文正公表彰朱子之书,天下乐为简易之说者。”①他沿着“简易”的方向,在朱熹的心说上兜圈子,为后来的心学一派开辟出道路。
许衡认为,人皆“禀天命之性为明德之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与尧舜神明为一”,但是在践履上一般人与尧舜圣人就不同了。他说:
众人多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能长存:或发于一件善念,便有被气禀物欲之私昏蔽了,故临事时对人旋安排把捉;未临事之前,与无人独处,却便放肆为恶。②
此谓善念到临事时就可以检验出来了。他特别强调慎独,在“与无人独处”时亦不能放肆为恶,必须谨慎而不敢疏忽才行。所以,他十分强调《大学》所讲的慎独工夫。他说:
幽暗之中,细微之事,人以为可忽者,殊不知其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更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所以,君子之心既常戒惧,而于此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虽人所不知,而独知之地,尤必极其谨慎而不敢忽。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③
他强调,“独是自家心里独知处;好善恶恶,实与不实,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
心里独自知道这等去处。君子必要谨慎,以审其几微。”①
在许衡看来,意念未发时之戒慎恐惧,能存天理之本然,其工夫是存养;由存养至慎独,能谨慎己所独知,从而遏人欲于将萌以至方萌。其工夫是省察。他说: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执之不使变迁。如此,则应物无少差谬。此所谓致知也,省察之事也。②
如能时时内自省察,无有不善,就能无愧于心。慎独是省察的前提和基础。气禀物欲之拘蔽于人既不容忽,人的尽心工夫就会连续不断,性中本然之理(善)即能永存。
许衡进一步指出,持敬则能身心收敛,身心常存。他说: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少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日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礼记》一书近千万言,最后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从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恶,皆从不敬上生。……这一件先能着力,然后可以论学。③
他所讲的这些,就是朱熹所讲的收摄涵养此心,敬之以恒,敬之忽失,就是常惺惺法,提心吊胆,便心不失其正。
在许衡看来,慎独为省察,持敬为涵养。在省察与涵养间他又加了个格物致知,这是许衡心学之独到处。他明确提出,“知其性是格物”④。此性是心体之性。知此心体之性,非格物不可。他说: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此解说个“穷”字;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说个“理”字。所以然者是本然也;所当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当然者是义也。每一事、每一物,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⑤
理固然为心体所内具,通过格物穷旭,如能自显心体所本具之理,此理即人之性。由知物之所当然,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物之所以然是其所当然之理由,此理由人于当初所未知。通过格物而致知。
由上可知许衡之心学体系了。他的结论是心与理为一。据记载:
问: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如何?先生曰:便是一以贯之。再问:理出于天,天出于理?先生曰: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①
由此,他便得出人、物后之于理的结论。他说:
有是理而后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诚有是理,而后成木之一物。表里粗细无不到,如成果实相似,如水之流满出东西南北,皆可体力而用行。积实于中,发理于外,则于恻隐、于羞恶,内无不实,而外自无不应。凡物之生,心得此理而后有形,无理则无形。②
由上可见,许衡为学皆朱子之义理,其特点是强调践履工夫,使心性真正体现于天理之中,达到完善的人格境界。所以,把许衡之学视为求心之学。
五 由郝经到王夫之
上述由黄榦开其端的朱子学中的三种思想倾向,在元代北方朱子学学派中都可以找到代表人物。元明北方朱子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思想基础,但是,北方朱子学派呈现出了朱子学中气论实学的思想倾向。当时北方朱子学派中的郝经、刘因等代表了这种倾向。
郝经(1223—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著《续后汉书》、《陵川集》等。早年“搜览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③,学问极为渊博。元初,郝经受学姚枢。先是姚枢在燕京(北京)建太极书院,请朱子学家赵复讲学于其中,姚枢得赵复所传;后来姚枢隐居苏门,许衡、郝经、刘因得其书而承其学。但是,郝经与赵复、姚枢的思想有所不同。例如,郝经把太极(理)看作“浑沦”,即看作是物。他在《太极图说》中认为,无极而太极者,包本末,贯隐显,一体用,极始终。他说:
浑沦圆转,而无上下内外,开廓布置而皆上下内外,含弘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混然一大活物,旁行而不流,无所不往而未尝去,居其所而变动无穷焉。圣人无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极。④
郝经这种对太极(理)的界说,就中孕育着气论实学的因素。今人龚道运说:
郝经言道或太极之为生生之理,乃就阴阳之气之生生之所以然而言。此理贯而主乎此生生之气流行中而为其理者,故曰理入于气。抑此理之入乎气,亦可谓其承先之气,以其后之气,而行乎气之中。所谓理不离气,即自理不离其所承之气与所起之气,如位于己化已息之气与方生方起之气之间而言耳。①
郝经对理气关系的认识含有二元论的倾向。
刘因(1249—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河北徐水(今保定)人。征诏为右赞善大夫,未几即辞归里,具有民族意识。有《静修集》行于世。
刘因在本体论上提出太虚元气说。他在《匏瓜亭》中说:
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造物全其真,世人若其味。虽得尽天年,惜坐无用器。伊谁窍混沌,大朴分为二。②
显然,这是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思想。他认为,事物都是由太虚之气所产生,并提出天地万物产生之前气为混沌之状。他虽未肯定气是本原,但其气论实学思想倾向比上述郝经更为明显。
刘因等人朱子学气论实学思想的倾向,到了明代前期的薛瑄(1389—1464年,号敬轩,山西河津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从朱熹的笃行出发,强调气的重要性。薛瑄在论到朱熹的《四书集注》时说:
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学者当以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③薛瑄明确指出,他的代表作是按照张载的《正蒙》方式写的。他对朱熹的
理气论进行了改造,把气提到和理同样的地位,具有了初步的气论实学思想。但是,他们仍未超出朱熹的思想体系。薛瑄的思想对明代中期的罗钦顺、王廷相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王学的批判和朱学的改造,继承张载的思想传统,把朱熹思想体系中的气学倾向发展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从朱子学中分化出来。
罗钦顺(1465—1574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的气论实学思想,是明末清初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居衡山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①《朱学论丛》,台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②《静修集》卷六。③《四书录》卷二。
南衡阳人)对理学进行总评判的先声。王夫之是中国气论实学的集大成者。因为王夫之的思想作为朱熹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所讨论的基本范畴大致相同而内涵相反。王夫之的思想是朱熹思想体系漫长衍变和分化过程的最后结局。在王夫之之后,朱子学尽管仍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占重要地位,但是就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史来说,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论实学思想已占有主导地位。
第三节 全国教育和书院
一 国学向乡校书院转化
朱熹思想流传全国后,其后学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们有的在朱熹有关的精舍、书院的基础上,或者自设精舍、书院,进行教育事业和学术活动,培养人才,撰述著作。把教育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是朱熹等书院活动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古代,教育事业是公立和私立相互补充而结合在一起的。到了朱熹活动的南宋以来,在异族和异教(主要是佛教)的侵蚀下,士风萎缩和教育经费困乏,公立教育事业更不能解决士风衰微的问题,更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于是私学有所发展。朱熹、张栻及其后学,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为中心,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教学理学,研究理学,恢复和发展儒学,排斥释道异端,振兴民族文化。他们所办的书院具有公私立学校相结合的性质。对此,韩国李朝李退溪说:
夫书院何为而设也?其不为尊贤讲道而设乎?自宋朝四书院之后,渐盛于南渡而大盛于元明之世。彼数代非无国学乡校而必更立书院者何也?国学乡校有科举法令之拘,不若书院可专于尊贤讲道之美意。故或因私立而国宠命之,或国命立之而择人教养也。若吾东方,则至当代而后始许立院,所谓因私立而国宠命者。窃仰圣朝之意,亦岂非慕数代之遗风而欲庶几,云云。①
李退溪的时代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叶。这是说南宋及其后的教育学校(国学乡校)具有公立和私立相结合的性质,并以此纠正科举法令之弊。朱熹等把书院由原来官家统制更多地转向民间私学为主导。这是其书院教育的又一大特色。
二 全国与朱熹相关的书院
在南宋元明清时代,理学家们的学院林立,形成为国家的教育网络。与朱熹有关的福建境内的书院上面已述。下面论述几处福建之外的、具有代表性的书院,以见一斑。①
白鹿洞书院 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是朱子学家进行讲学活动的重要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又名白鹿洞书堂、白鹿书院、朱晦庵书院。最初为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渤及其兄李涉隐居读书之地。传说李渤曾养一白鹿自娱,故被时人称为白鹿先生。后来,他任江州刺史,在一石洞里建造一台榭,以其别名“白鹿先生”而命名为“白鹿洞”。南唐李昇昇元四年(940年),白鹿洞正式辟为“白鹿洞国庠”,又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任洞主,执掌教授之职,并置学田授徒,学徒常数十百人。宋初改名为“白鹿洞书院”。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赐予国子监印本“九经”。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于书院故址建造学舍10余间,称“白鹿洞书堂”。不久毁于兵火。
白鹿洞书院之兴盛并扬名于天下,实赖于朱熹。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军守。当时书院已毁,朱熹疏请修复。重修后的书院,规模庞大,共有殿宇书堂360余间,其中以圣礼殿为中心,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祠、先贤祠、忠节祠等。朱熹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②,成为后来全国书院教育规章制度的范本,对后世书院体制的建设以及书院教育的推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吕祖谦撰《白鹿洞书院记》,叙其始末。始称其为四大书院之一。朱熹自任洞主,讲学其中,并邀请陆九渊等到此讲学,史称“南康之会”。陆九渊的讲题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据说听众中有人被陆九渊的讲说感动得落泪。这种讲学活动对于推动学术思想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书院毁于兵火。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重建。国子监祭酒胡俨为文记之。此后,程敏政、李梦阳等屡有修缮。胡居仁、李梦阳、王阳明等先后讲学于此。神宗万历(1573—1620年)初,张居正废书院,旋复。清代,该书院屡有修复,并被保存至今。
龙光书院 在江西丰城荣塘剑池庙左,亦作“荣光书院”。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邑人陈自俯创建①,“四方来学者三百余人”②,有六经楼、仰止堂、讲堂、戒规堂等建筑。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往潭州访张栻途经于此,在此讲学。朱熹题有《丰城荣光书院》诗③。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应丰城门人熊世基、熊世琦兄弟之请,为“其所构龙光书院之堂”撰写《龙光书院心广堂记》,其中有曰:
丰水之夏阳熊世基、世琦执经来学之明年,乾道庚寅岁(按即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也,请铭其所构龙光书院之堂。熹榜其间曰“心广”,且嘱以敷畅厥义。复之曰:“人生两间,孰无此心?”心者,贯万事,统万理,主宰万物者也。然则若之何而不广乎!克其所以为广累者,则心广矣。④
濂溪书堂 在江西九江城南濂溪巷,亦名“濂溪书院”。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建,后遭兵毁。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江州知州潘兹明、通判吕胜己重建,朱熹为之撰《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⑤是记讲了理学的基本思想,以及濂溪书堂的缘由。其中有曰:
夫天高地下,而二气五行纷纶错糅、升降往来于其间。其造化发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则仁、义、礼、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而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然气之运也,则有醇漓判合之不齐;人之禀也,则有清浊昏明之或异。是以道之所以讬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亿度而强探也。《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矣,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先生)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明其川曰“濂溪”,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按即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己,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为记。⑥
这里开头讲的理学基本思想的源流,是由《河图》、《洛书》、孔子等以至于周敦颐的,然后又由二程以至于朱熹本人。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四月六日,朱熹在知南康军任满,归家途经江州之时,曾在此讲学,“拜濂溪先生书堂遗像”,随行的有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祁真卿、昊兼善、许子春、胡莘、王朝、余隅、陈士直、黄榦、张彦先等一批弟子,以及会稽僧志南、明老等。①刘子澄请朱熹“为诸生说《太极图》义”,周敦颐之“曾孙正卿、彦卿,玄孙涛为设食于光风霁月之亭”。②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朱熹门人赵崇宪知江西江州,曾筑室26楹于濂溪书院,作为书院诸生学舍。此后,元、明、清诸代均对此有修复。
东山书院 在江西余干县冠山东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赵汝愚及从弟赵汝靓建。赵汝愚之子崇宪、崇度皆朱子门人,曾延请朱熹讲学其中,朱熹为其“云风堂”书匾。③后来,赵“汝愚卒,朱子来吊,复馆焉。后为胥吏所据,邑人李荣庭鬻产赎之。”谢枋得为记。④由此可见,朱熹到东山书院至少有两次。
怀玉书院 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金刚岭之阳。北宋杨亿曾于此建怀玉精舍。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陆九渊、汪应辰曾讲学于此,于是当政官吏和朱熹门人便在此建立书院,以供四方来学之生。⑤朱熹说:
秋冬间无事,或可出入。其思承教。……闻怀玉山水甚胜,若会于彼,道里均矣!⑥
此书写于淳熙元年(1174年)。此言朱熹与吕祖谦“怀玉之约”。但是,到了秋间,两人均因故未前往。他又约“迟至明年”、后年。朱熹说:
熹还家数日,始登庐山之顶,清旷非复入境,但过清难久居耳。至彼,与季通方议丹丘之行,忽得来教,为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至鹅湖追逐,入怀玉深山,坐数日也。损约收敛,此正区区所当从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应者,自承警诲,什损四五矣!自此向里,渐渐整治,庶几寡过,但恐密切处不似外事易谢绝也。①
朱熹“怀玉之约”终有否成行,未有明确记载。而朱熹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十一日,侍讲罢归路过玉山,县令司马迈设讲席,朱熹为诸生讲学,遗存有《玉山讲义》。朱熹到过怀玉山讲学,是肯定的。
银峰书院 在江西“德兴县市延福坊。宋淳熙间(1174—1189年)邑人余瀚、余渊延朱子讲学其中。明崇祯间(1628—1644年),裔孙应馨改建于肯堂下”。②
草堂书院 在江西玉山县北怀玉山下。据方志载:
朱子讲学于此。有青山缘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相传朱子题山下酒舍一联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旁青山不买柴。”即其地也。宋末书院废。斗山玉奕与其子介翁结庐居此。③此仅方志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处谓朱熹一联语,未见《朱子文集》,值得注意。
盛家洲书院 在江西丰城县东蓝家巷。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崇安往潭州访张栻,顺道讲学于此。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邑人盛温如在此建书院。④据方志载,有朱子《盛家洲》诗二首,其一云:
湖上阑干百尺台,台边水殿倚云开。洪桥人隔荷花语,玉碗水盘进雪来。⑤
鹅湖书院 在江西铅山县鹅湖山下,原为鹅湖寺。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人相约会讲于此,因学旨与陆氏兄弟不合而罢,史称“鹅湖之会”。对此,朱熹说:“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也。”⑥吕祖谦说:“某以五月半后,同朱丈出闽,下旬至鹅湖。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⑦朱熹有《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一首,曰: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①
后人于朱陆论辩处建四贤祠以祀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
书院前排建筑中悬有“道学之示”的御匾,四贤祠中有“顿渐同归”匾。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疏请赐额,赐曰“文宗”,故又名文宗书院。元代迁至铅山城内(今永平镇)。著名学者吴师道、程端礼等先后任山长。元末毁于兵火。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巡抚韩雍、广信知府姚堂对鹅湖寺重新修葺。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命铅山知县秦礼于旧址重建。明代宸濠之乱,书院学舍几乎毁坏殆尽。及至明末,几经重修而得以不堕。清世宗顺治十年(1653年),江西巡抚蔡士英捐资重建,并列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地方官潘士瑞曾加修葺。康熙五十四年,令尹施德大加修建。李光地记曰:
书院之建,实为国家学校相为表里。李渤高士尔,朱子犹倦倦焉。今使先贤遗址,焕然重修,江右故理学地,必有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贤者。②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亲书“穷理居敬”额。高宗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郑之桥重加修葺。编有《鹅湖讲学会编》。仁宗嘉庆十七年(1812年),吴嵩梁为山长,编撰《鹅湖书院田志》。文宗咸丰年间(1851—1861年)毁于兵火。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重建。清末改为鹅湖师范学校。
钟山书院 在江西婺源。南宋孝宗淳熙初年(约1175年),县人李缯(字参仲,号钟山)建。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初次回婺源省亲扫墓,识得李缯。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省亲扫墓,与表兄程允夫至该书院,“徜徉其间,讲论道义,谈说古今,觞咏流行”,并讲学其中。③据《语类》记载:
先生(指朱熹)游钟山书院,见书籍中有释氏书,因而揭看。先君问:“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无所得。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备具,不必它求。”④
隆冈书院 在江西南昌“府城南四十里,形如象尾相近,有澹冈及隆冈。
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8年),进士刘邦本建隆冈书院,其裔孙藏有朱子所题四景诗”。淳熙八年(1181年)四月,朱熹由南康军归闽,途次于此,作《隆冈书院四景诗》。诗分为春、夏、秋、冬四景,每景七言律诗一首。①未知此与近年在福建古田发现的朱熹《四景诗》是否相同。
双桂书院 在江西德兴。据方志载:“双桂书院在游奕坞,相传朱子赠程烨、程燧兄弟诗,有‘两种天香手自栽’之句,书院之名由此。”②朱熹此诗为《题程烨、程燧兄弟双桂书院》,原载清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全诗为:“君家构屋积玉堆,两种天香手自栽。清影一帘秋澹荡,任渠艳冶斗春开。”③
据考证,此诗应为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前往婺源省墓前后所作。程烨、程燧当为朱子门人,生平缺考。“按(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二《书院》:‘蒙斋书院,朱子门人程端蒙讲学所,旧在德兴县游奕坞。’而程烨兄弟双桂书院亦在游奕坞,似程烨兄弟与程端蒙为同宗之戚,自必相识。朱熹绍兴二十年归婺源省墓,即尝经德兴拜谒名诗人董颖,德兴士子已有来执礼问学者。淳熙三年再归婺源,程端蒙又特自德兴抠衣裳来谒,程烨兄弟或亦在其时同见朱熹并请赠诗”。④
岳麓书院 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始创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创建者为潭州太守朱洞。因其址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故名。初创时,书院设有讲堂5间,斋舍52间。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对书院作了扩建,并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置田产,授徒讲学,当时学生定额约为60人。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赐《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由此形成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等基本规则。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后,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也扩大至100余人。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拜国子监主簿,并赐“岳麓书院”额。由此书院称誉天下,成为地方最高学府,位在潭州州学之上。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书院因战乱,毁坏严重,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并请著名学者张栻主持教事、讲学其间,岳麓书院遂达到鼎盛时期。宋代理学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的许多学者也曾在岳麓书院学习或讲学,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活动基地。一时之间,前来求学的士子大增。
乾道三年(1167年)秋,朱熹从福建来访张栻,并在书院会讲《中庸》,史称“朱张会讲”。据传,当时听众达几千人。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张栻去世。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因书院失修而进行修复并扩建。请醴陵贡生黎贵臣为书院执事,朱熹又将他手订的《白鹿洞学规》用作岳麓书院学规。
南宋末至明初,书院几经焚毁。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书院得以扩建,并置学田2000余亩,规模空前。嘉靖以后,王阳明门人相继讲学于此。明亡,书院亦毁于战火。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赠以御书“学达性天”额及经史诸书,因建御书楼。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御书“道南正脉”额赠之,书院得以重振。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南轩书院 在湖南衡山南岳山后,宋张栻建。张栻因父浚“奉诏居永州,栻往来省侍,受业于五峰胡宏之门,置书院于岳麓山后”①。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张栻与朱子同游,讲学于此。”②
城南书院 在湖南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建。“城南书院”门额为其父张浚手书。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与门人范念德、林用中“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③讲学之余,朱、张两人相互唱和,朱熹有《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④原诗的朱熹手迹收入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子遗墨》一书中。⑤
邺侯书院 在湖南衡山烟霞峰下。唐代邺侯李泌隐居于此读书、藏书,其子蘩于南岳庙之左侧建“南岳书院”。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改称“邺侯书院”。明人重修,又改称“集贤书院”,合祀唐宋诸贤于其中。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年),复称“邺侯书院”。⑥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张栻在“岳麓会讲”之余,曾同访烟霞遗迹,并赋诗以纪。朱熹有“山道榛芜大道荒,令人瞻望邺侯堂。怀贤空自悲今昔,泪滴西风恨夕阳”的诗句。①
石鼓书院 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中州人李宽始建。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邑人李士真重建。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赐“石鼓书院”额,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②
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部使者潘畤、提刑宋若水相继修建。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应宋若水之请,为之撰写《衡州石鼓书院记》。朱熹告诫诸生不要被“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的“学校科举之意乱焉”,而要“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书院立石刻碑以传。③
姚江书院 在浙江余姚。当地有姚江,故名。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年),邑人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建于半霖,祀王阳明。邑中士有志节者,均寝食其间,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课,学阳明学,溯洙泗,逮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以申明良知之学。史孝咸主讲10年,相传“和平光霁,以名教为宗主”,由此士风大振。沈国模尝以80岁高龄,每岁自四明山至书院,为诸生讲习。黄宗羲晚年亦曾主讲于此。
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县韦钟藻移建于城南巽水门内角声苑旧址,并请著名理学家邵廷采主持讲席达17年。以讲求程朱理学为主,又竭力调和朱陆学说。钱仪吉《碑传集》详细记载了当时该书院讲会之情景。世宗雍正九年(1713年),浙江总督李卫重修。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6年),增建庑院。今有《姚江书院志略》传世。
逸平书院 在浙江江山,原名“南塘书院”。南宋高宗绍兴初年(约1132年),儒士徐存(字逸平,号诚叟,杨时门人)建,被后人称为“逸平先生与朱考亭讲学之所”。④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在中进士第后回闽途中,首次造访徐氏。朱熹在《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中曰:
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①
朱熹在《江山县学景行堂记》曰:
徐公诚叟者,受业程氏之门人,学奥行高,讲道于家,弟子自远至者,常以百数。其去今不远也。吾意大山长谷之中,隘巷穷闾之下,必有独得其传而深藏不市者,为我访而问焉。②
明方豪《逸平书院记》中谓,“吾邦有先正曰逸平先生者,徐姓,存名,诚叟其字。受业龟山,得程氏之学,与朱子实相友善,尝讲道于南塘书院。逸平既殁,朱子往吊焉。书院已为毛氏墓田,因赋诗寄哀,有‘徐子旧书址,毛公新墓田’之句。”③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知县吴仲将书院迁至城西骑石山麓,更名逸平书院。④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年),书院毁于兵火。
稽山书院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任浙东提举,在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卧龙山西岗讲学,后马天骥于此处建祠祀之。据《于越新编》所纪:
宋朱文公尝司本郡常平事,讲学敷政,以倡多士。三衢马天骥建祠祀之,其后九江吴革因请为书院。⑤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年),得以增葺。后毁。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知县张焕发重建于旧址之西麓。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阳明弟子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后为瑞泉书院。明王守仁为之记。⑥
丽泽书院 南宋吕祖谦、吕祖俭兄弟创立,在浙江金华。“丽泽”原指“两泽相连,润说之盛”,后借喻朋友之间讲习切磋。吕祖谦、吕祖俭兄弟晚年创设丽泽书院,讲学会友。吕祖谦常邀请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讲学。吕祖谦编著《近思录》(与朱熹合编)等,供学徒学习。还手订《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①据传,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该书院,在当时的教育界及思想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吕祖谦在该书院所讲内容,由其弟祖俭等人编为《丽泽讲义》。
吕祖谦死后,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吕氏门人请修书院,官府允之。建吕祖谦祀室及遗书阁,并开始刊刻图书。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吕氏门人又将吕祖谦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以吕祖俭配祀。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知州许应龙迁书院于双溪之畔,奏请理宗御赐匾额。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又迁至旌孝门外印光寺故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何基、王柏、金履祥先后任山长、主讲,四方来学者甚众。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又有重修之举。后毁于明末。
清全祖望说,“明招学者,自成公(祖谦)下世,忠公(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岳麓书院)之泽,并称克世……而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②说明该书院在培养人才、保存古代文献等方面有诸多贡献。
樊川书院 在浙江黄岩杜家村。《赤城新志》载:“晦庵先生与南湖二杜公讲学之地。”南宗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任浙东提举时,巡历至台州,曾至黄岩。“在县北六潭山,朱文公尝著书其麓,名为小樊川,题曰溪山第一”。③黄岩的朱子门人有杜贯道、杜煜、杜知仁、池从周等,后杜知仁侄孙杜范建“紫阳书院”,后有朱文公祠。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知县刘宽更名为樊川书院。
文献书院 在浙江黄岩委羽山。《赤城新志》曰:
元枢密副使刘本仁建。以朱文公尝施教于台(州),杜清献公得其传,因祀文公于此,而以清献配焉。危素、朱右俱有记。④
杜清献即杜范,字成之,朱子门人杜煜、杜知仁从孙。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官至右丞相。《宋史》杜范本传谓其“少从其从祖烨(煜)、知仁游,从祖受学朱熹,至范益著。”⑤可见杜范本人并未直接从学于朱熹。后人以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官浙东提举时,曾巡历台州,讲学黄岩,而杜范又是其再传弟子,故建此书院以祀。
龙津书院 在浙江奉化,原名“龙津馆”。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泊舟于此,率诸生讲学焉”。①理宗景定初年(1260—1264年),立龙津书院于此。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改名“文公书院”。“知州李炳移建于州之宝鹿山,山长任士林为记”。②
紫阳精舍 在浙江诸暨旧县署侧。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官浙东提举时,曾延当地名士杨文修“谈名理及医学天文地理之书,数日去”。“紫阳精舍,一名义安精舍,在旧县暑例。宋朱子为常平使者,召杨文修与谈理学,因此宿焉”。③后人因建精舍以祀之。
泳泽书院 在浙江上虞,元世祖至元年间(1279—1294年)创于西溪湖滨,方枢密移于金壘山东。因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曾讲学于此而立祠祀之。④
明善书院 在浙江松阳西20里。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为“修举赈荒事”至松阳。时邑人叶震“隐居教授于家塾,执所业见焉。朱子与语而有契,为讲《论语》、《孟子》”。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其后人叶再遇即其家塾而扩充之,称明善书院,以祀朱熹。⑤
独峰书院 在浙江处州缙云仙都山。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朱熹任浙东提举时,因连续上疏弹劾唐仲友,未报,“二十二日入处州缙云县界讫,累日以来,恭候威命,未有所闻”。⑥于是,到缙云县东仙都,“徜徉于此山,以伺朝旨,有‘于此藏修为宜’之语”。“爱其山水似武夷”。⑦在游历唐代诗人徐凝故居时,作《追和徐氏山居韵》绝句一首。诗云:
山岫孤云意自闲,不妨王事似连环。解鞍磐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山。⑧
并曾在此讲学。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邑人叶嗣昌于仙都山独峰前建此书院以祀朱熹。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邑人潜说友即旧址扩而新之。
美化书院 在浙江缙云东美化乡。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时,曾在此讲学。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年),知县陈大猷、县尉陈实因建书院以祀之。①
五云书院 在浙江缙云五云山下。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6年),楼如浚建。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知县方润重建。因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曾到仙都讲学,邑人曾建独峰、美化两书院祀之,但年久均废,因立此书院继祀。②
鄮山书院 在浙江宁波府城西五里,元邑人赵儒(应为赵寿)建,设山长主之。袁桷为记。“元大德三年(1299年),乡儒赵寿建为祠,以祀朱子,久圮。”③
朱熹生前有否经履宁波,未有明确记载。但是,朱熹曾在浙东任职,不能排除其未到过宁波。赵寿建此书院,起因乃其祖赵善待(字时举)曾从朱熹学。④
包山书院 在浙江开化北。南宋孝宗乾道末年(约1173年),邑人汪观园、汪杞兄弟建“逍遥堂”,又名“听雨轩”,以课读子弟。汪观国二子汪湜、汪泓均从吕祖谦学。
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朱熹回江西婺源省亲,曾与吕祖谦相约于此,论辩讲学数日,两人讲论的课题涉及《毛诗序》、《易》、《春秋》等。朱熹有《汪端斋听雨轩》七律一首:
试问池堂春草梦,何如风雨对床诗。三薰三沐事斯语,难弟难兄此一时。为母静弹琴几曲,遣杯同举酒千卮。苏公感寓多游宦,岂不临风尚尔思。⑤
听雨轩因朱、吕讲学而闻名,汪观国之子汪泓“立书院以祀朱、吕二先生,后孙继荣请于朝”。⑥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御赐“包山书院”匾额。
五峰书院 在浙江永康方岩寿山坑。因寿山坑有鸡鸣、覆釜、瀑布、固厚五峰而得名。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吕祖谦、陈亮等曾在固厚峰下石洞中读书讲学,时称“三贤”。堂侧摩崖上,有陈亮手书“陈龙川、朱晦翁、吕子约尝同游”,有朱熹手书“兜率台”石刻。①
明世宗嘉靖初年(约1523年),“邑人应典因为祠以祀三贤,知县洪垣更为书院”。②
石洞书院 在浙江东阳。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邑人郭钦止(德谊)建。其子津、浩均为朱子门人。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二月,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曾到此讲学,赠送所著《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后郭津曾将书院重修,并请朱熹为之撰记题匾。朱熹说:
书院规模,且随事随力为之,却就事实上考察整理,方见次第,不须如此预先安排。记文匾膀,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见浮浅外驰之验。若于学问全体上切己处用得功夫,即气象自当深厚宏阔矣。③
朱熹虽不曾为此书院撰记,但却题写了“洞山”、“月峡”、“流觞”刻于石壁之上,并为书院创建者郭德谊书写《郭德谊墓志铭》④。叶适有《石洞书院记》。⑤
月林书院 在浙江上虞,宋潘畤建。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官浙东提举时,潘氏曾延朱熹在此相与讲明性命之学。从学者有潘畤之子潘友文、潘友端、潘友恭及孙邦仁等。⑥后朱熹离任,曾举潘友恭以自代。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潘畤逝世,朱熹撰文祭祀。⑦
月泉书院 在浙江浦江西北二里。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浚泉建亭,名为泉亭。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正月,朱熹以浙东提举巡历过浦江,曾讲学于此。朱熹说:“(臣)于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县界,历义乌、金华、武义县。”⑧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知县王霖龙建“月泉书堂”,亦名“月泉精舍”。据记载:
以是州东莱先生吕成公讲道丽泽、紫阳先生朱文公尝提举浙东常平,行部过此,且与成公友善,遂于此地阐明正学。乃祠二先生于月泉精舍,
使学者瞻仰兴慕,肄业其中。①
元代升为书院,置山长。元明两代,历经重修。
瀛山书院 在浙江淳安北40里银峰之麓,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邑人詹安于此建双桂书堂,收詹氏弟子入学。其孙詹仪之,乃朱熹门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其后人詹骙中状元,故取“登瀛”之意,改书堂名为瀛山书院。据方志载:
瀛山书院,在县治北四十里。……宋熙宁间邑人詹安辟,其孙仪之与朱子论学于此,朱子有“半亩方塘一鉴开”之句。明隆庆三年,知县周恪访名贤遗迹重建,王畿为记。②
今学者据方志、淳安《詹氏宗谱》、明王畿《瀛山书院记》以及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南州后学闵鉴所书方塘诗石碑,著文论证方塘在淳安瀛山③;或言朱熹生前曾分别于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乾道九年(1173年)、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三次到瀛山书院讲学。④对此,束景南考证说:
《朱文公文集》卷二及卷三十九《答许顺之》书十,均有此诗而无此题(按指《方塘诗》),“惟有源头活水来”均作“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名《观书有感》非访詹虚舟仪之有感而作,宗谱、书院记均不可信。遍考朱熹生平仕历游踪,断无往淳安游访之可能,石碑诗题之伪不待一辨。……后世各地据朱熹此诗附会“方塘”并构“天光云影亭”甚多,以予只就方志所见,不下五六处,淳安瀛山不过附会之一也。⑤
考《朱子文集》,朱熹与詹仪之的书信凡五通,未明确讲其到淳安讲学。⑥
宗晦书院 在浙江乐清县治东。宋建,以祀朱熹。旧名艺堂书院,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改名宗晦,取宗晦庵之义。方志载:“宗晦书院,在(乐清)县治东。宋杨艺堂立,有文公祠,故名。”⑦
南山书院 在浙江宁波,为宋代沈焕(1139—1191年,谥号端宪)讲学处,宋理宗赐额。朱熹与沈焕谈道住宿于此。时比白鹿洞书院。①朱熹与沈焕的关系,朱熹说:
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熹所识者杨敬仲、吕子约,所闻者沈国正(焕)、袁和叔(燮),到彼皆可从游也。②
“所识”乃指见面相识,“所闻”则未尝见面。陈来考定此书约写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滕璘官鄞县尉赴任之际③,时已是朱熹官浙东提举之后,而此后朱熹再也未曾到过浙东。因此,上引所谓“谈道住宿”于南山书院是有问题的,应该进一步研究。
东屿书院 在浙江台州温岭。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邑人丁少云建。有松山、南麓诸亭池、楼阁及“东屿书房”。少云子、进士、青田县令丁木又建云海观、台榭岩径等70余所,为浙东冠。④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浙东提举,应丁木之请,作《题东屿书院》五言八句一首。诗曰:
书房在东屿,编简乱抽寻。曙色千山晓,寒灯午夜深。江湖勤会面,
坐卧独观心。秋浦瓜期近,何当寄此吟。⑤
石门书院 在浙江青田石门洞。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提举浙东,循行至此,有汶上之兴。元惠宗至正年间(1279—1294年),廉访使王俣始即谢客堂故址建。“汶上之兴”令人不知所云。考清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有《训蒙绝句》百首,其中第四十五首题为《汶上》。故所谓“汶上之兴”,殆指朱熹循行至此,触发了诗兴,留下了绝句一首。诗云:
仕非其地宁无仕,此地还他德行人。彼以势邀吾自逝,丈夫无欲气常伸。⑥
从诗意看,比较符合朱熹在浙东任上因连续弹劾唐仲友而未能奏效的激愤心情。
据方志载:“石门书院,在县西七十里石门洞。《续文献通考》:宋淳熙九年,朱文公提举常平至此,欲居之。元至正中廉访副使王俣始即谢客堂故址建,不久圮。”①所载与光绪《紫阳朱氏建安谱》大同小异。因朱熹有《汶上》诗,此书院可列入因朱熹题诗后所建之书院。
紫阳书院 在徽州城(今安徽歙县)南门外,宋理宗亲笔题额。徽州城南五里有紫阳山,朱熹父朱松少尝在此山读书,及至入闽之后亦常思念此山,曾刻以“紫阳书堂”作为自己的印章。后来,朱熹寄寓福建崇安五夫里时,曾“牍所居之厅事堂曰‘紫阳书堂’”②。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两次回婺源扫墓祭祖。“其时,思返旧庐,滞留数月,执弟子礼者三十人”③。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朱子门人赵师端为徽州知府,立朱文公祠堂于郡学,黄榦为之记。④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因郡守韩补之请,于城南门外建为书院,宋理宗赐额“紫阳书院”,教授诸葛泰为记。书院依山傍水,前为书楼,后为宸奎阁,其规模宏大、壮观。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又加以重建,方回为之记。⑤
附注
①《宋元学案》卷六四《潜庵学案·附录》。
②《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
①《宋史》卷四三〇《李燔传》。
②《勉斋集》卷八《书朱子行状后》;《宋史》卷四三〇《黄榦传》。
③《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
④《宋史》卷四三八《何基传》;《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⑤《元史》卷一八九《许谦传》。
①《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祖望按语》。
②《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③参见《元史》卷一五九《窦默传》。
④《八闽理源流》卷二《元朝》。
①[明]朱衡:《道南源委》卷首。
②[明]戴铣:《朱子实纪》卷四《年谱》。
①[明]戴铣:《朱子实记》卷九《褒典》。
②光绪《重修婺源县志》卷二〇《朱子世家》。
③佚名:《松下杂钞》卷下。
④转引自冒怀辛:《朱熹学派在福建的流传和影响》,《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
①蒙培元:《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②《黄氏日钞》卷九五《读抱朴子》。
③《勉斋集》卷七《中庸总说》。
①牟宗三:《引言》,《阳明学讨论会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89年版,第4页。
②《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
③咸丰《鄞县志》卷二四《寓贤》;《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
④《日钞》卷九五《读抱朴子》。
①《日钞》卷八二《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
②《日钞》卷八二《抚州辛未冬至讲义》。
③《日钞》卷八五《回陈总领》。
④《朱子语类》卷四《人物之性气质之性》。
⑤《日钞》卷九五《读韩文》。
①《日钞》卷五九《祭添差通判吕寺簿》。
②《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③《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①转引自《青鹤》第2卷第21期,1936年9月16日。
②以上参见[日]别府淳夫:《朱次琦与康有为——晚清的朱子学研究》,1987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第九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③《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页。
④《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⑤《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①《宋元学案》卷首《序录》。
②[宋]程钜夫:《楚国文宪公雪楼先生文集》卷一四。
③《饶双峰讲义》卷一〇《孟子·公孙丑上解》。
④《饶双峰讲义》卷一〇《中庸解》。
①《饶双峰讲义》卷一五《附录》。
②《饶双峰讲义》卷二。
③《饶双峰讲义》卷八。
①《饶双峰讲义》卷一五《附录》。
②《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③《朱子文集》卷一四《乞修三礼札子》、卷五四《答应仁仲书》。
①《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②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5页。
③《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④《草庐全集》卷四《无极太极说》。
⑤《草庐全集》卷三《答田副使第三书》。
①《五经纂言·易纂言·文言传》。
②《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③《草庐全集·外集》卷二《杂识》五。
①《草庐全集》卷四《主敬堂说》。
②《草庐全集》卷二《答王参政仪伯问》。
③《草庐全集》卷六《朱肃字说》。
④《中庸》。
⑤《草庐全集》卷六《陈幼实思诚字说》。
⑥《学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
①《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卷一〇《元诸子·吴草庐》,《增补退溪全书》第3册,第508页。
②《草庐全集》卷八。
③《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祖望案语》。
④[清]娄谅:《康斋先生行状》。
⑤《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卷一〇《元诸子·赵江汉》,《增补退溪全书》第3册,第511页。
⑥《宋元学案》卷九〇《鲁斋学案·祖望按语》。
①《鲁斋遗书》卷四《大学直解》。
②《鲁斋心法》,第15~16页。
③《鲁斋全书》卷四《答丞相问论大学明明德》。
④《鲁斋心法》,第3页。
⑤《鲁斋全书》卷三。
①《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
②《鲁斋全书》卷三。
③《宋元学案》卷九〇《鲁斋学案·文忠郝陵川先生经》。
④《陵川集》卷一〇。
①《拟与丰基郡守论书院事》,《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41~342页。
①本节参见潘富恩主编:《宋明理学》第4册,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朱子文集》卷七四。
①同治《丰城县志》卷七[明]徐即登:《重建龙光书院记》。
②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略·书院》。
③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五四。
④转引自同治《丰城县志》卷二。
⑤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二《建置略·书院》。
⑥《朱子文集》卷七八。
①[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二。
②《朱子文集》卷七《北山纪行十二章章八句》之七自注。
③《宋元学案》卷四九《晦翁学案》。
④[清]谢枋得:《叠山记》卷二《东山书院记》;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图·书院》。
⑤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略·书院》。
⑥《朱子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三五》。
①《朱子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四〇》。
②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略·书院》。
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略·书院》。
④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略·书院》。
⑤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〇。
⑥《朱子文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一》。
⑦[宋]吕祖谦:《东莱集》卷五《答潘叔度一九》。
①《朱子文集》卷四。
②《重修鹅湖书院记》。
③《朱子文集》卷八三《跋李参仲行状》。
④《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
①雍正《江西通志》卷七、一五四;乾隆《南昌府志》卷一七;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
②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建置·书院》。
③《朱熹集·外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①光绪《南岳志》卷一七《书院》。
②光绪《湖南通志》卷六九《学校·书院》。
③同治《岳麓志》卷三。
④《朱子文集》卷三。
⑤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⑥光绪《南岳志》卷一七《书院》。
①《南岳唱酬集·自上封下福岩道旁访李邺侯书堂山路榛合不可往矣》。
②光绪《南岳志》卷一八《书院》。
③《朱子文集》卷七九。
④同治《江山县志》卷四《学校》。
①《朱子文集》卷八一《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
②《朱子文集》卷七八《衢州江山县学记》,参见[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七。
③[明]方豪:《逸平书院记》。
④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
⑤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七《学校》。
⑥《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曾经阁记》。
①《乾道五年规约》。
②《宋元学案》卷七三《丽泽诸儒学案》。
③拙著:《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④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七《学校》引《赤城新志》。
⑤《宋史》卷四七三《杜范传》。
①拙著:《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②万历《紫阳朱氏建安谱·书院总纪》。
③嘉靖《诸暨县志》卷二七《人物·杨文修》、卷四二《坊宅》。
④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七《学校》。
⑤[明]王祎:《王忠文集》卷一〇《明善书院记》;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九《学校》。
⑥《朱子文集》卷一九《又乞罢黜状》。
⑦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九《学校》。
⑧[元]陈性定:《仙都志》卷下。
①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七《学校》。
②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光绪《缙云县志》卷二。
③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七《学校》引嘉靖《宁波府志》。
④[清]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九。
⑤弘治《衢州府志》卷一三。
⑥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
①拙著:《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②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
③《朱子文集》卷五四《答郭希吕四》。
④《朱子文集》卷九二。
⑤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
⑥光绪《上虞县志》卷三〇。
⑦《朱子文集》卷一九《举潘友恭自代状》、卷八七《祭潘左司文》。
⑧《朱子文集》卷一六《奏巡历婺衢救荒事件状》。
①嘉靖《浦江志略》卷六。
②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
③《朱熹的方塘诗考》,《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
④《朱熹在淳安事迹考略》,《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⑤《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⑥《朱子文集》卷二七《与詹体仁书》四通、卷三八《答詹体仁》一通、卷八七《祭詹侍郎文》。
⑦嘉靖《温州府志》卷一《学校》。
①参见《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②《朱子文集》卷四九《答滕德粹书一一》。
③《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④嘉靖《太平县志》卷八。
⑤原载嘉靖《太平县志》卷八、戚鹤泉:《台州外书》卷一三;《朱熹集·外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⑥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①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学校》。
②[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一。
③[清]王梓材等:《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九汪佑:《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
④[宋]黄榦:《勉斋集》卷一七《徽州朱文公祠堂记》。
⑤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九二《学校·书院》;[元]方回:《桐江集》卷二《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