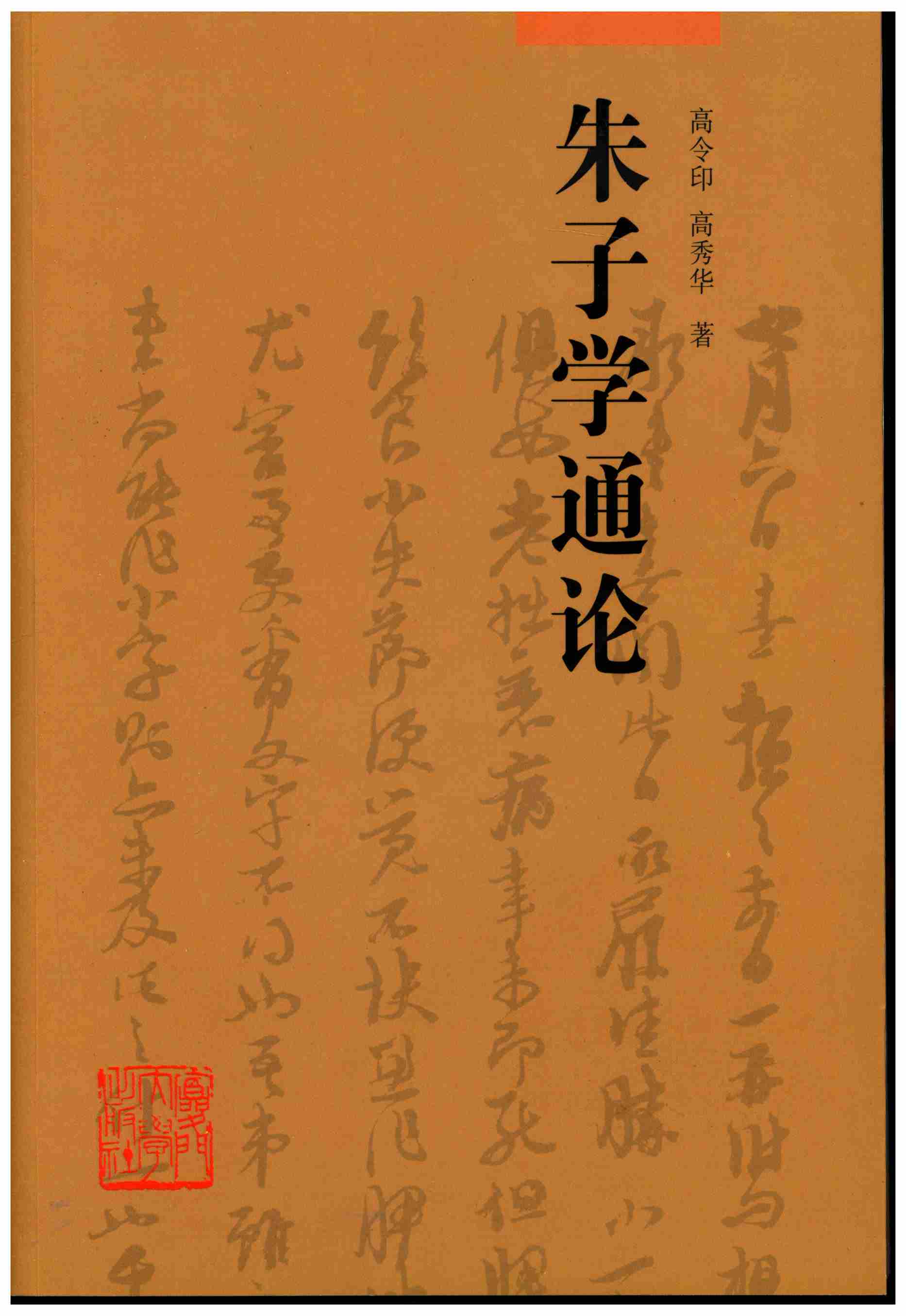内容
一 穷经观史求义理
中华民族历代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通过汉字这一传播媒介充分地记录表达出来,形成浩如烟海的典籍。对这些典籍,前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史是指以反映历代国家历史、典章制度、土地等的文献;子是指历代学者的诗、文的汇集;集是指类书、丛书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典籍的汇集。这些古代典籍,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结晶。
上述学科,过去集中于文、史、哲(包括宗教)三个最为重要的学科。古人治学不细,把诸学科都纳入经学的范围内。经、史、子、集分类法是由经学衍化出的。清代学者又提出史学最具有综合性,认为它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所有学术领域,因为每个学科都需要首先考察历史发展,而且中国古代典籍都可以运用于历史的研究中。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得到著名学者龚自珍、章炳麟等的赞同。①他们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朝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贤们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造出来的。
朱熹也是把经学、史学,联系在一起的,提出“穷经观史以求义理”、“多读经史,博通古今”、“经史阁”等,认为“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时之用矣”②。经学、史学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
朱熹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其理论的提出,几乎都与他的经学、史学分不开,他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都蕴含有历史学。当时没有学科划分,朱熹结合时代的需要,通过对诸经的训解阐释而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其哲学等思想,都是后人根据现代学科分类及学科名词,通过研究朱熹经学、史学而提出来的。《朱子语类》卷一四至九二都是直接讲朱熹的经学、史学的,占整个《朱子语类》的一大半。其余的内容也与经学、史学有密切联系。朱熹的其他著作,大多是对儒家经书、史学的注释和阐发,如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四书或问》、《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古今家祭礼》、《仪礼经传通解》、《孝经刊误》等。《朱子文集》中的诸多书信答问,大量的是与当时的众多学者讨论经学、史学的问题,而《文集》中的杂著,大部分内容也是对经学、史学的论述。这说明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主。他是在对经书的阐述基础上发挥其历史观。
二经学
经学是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战国时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至汉代,经学大盛。然经学之名则见于《汉书》:兒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③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现实社会服务。离开了儒学,便无经学。而离开了经学,也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既不能把经学与儒学混为一谈,亦不可把二者截然分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先秦儒家经典主要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有目无书,说法不一,汉代人删去而增进《孝》《论语》,合称七经。唐代人又扩至九经或十二经:把《礼》析为《周礼》、《仪礼》、《礼记》,再增进《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尔雅》。宋代人增进《孟子》,总称“十三经”。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经书的选集。历代对经书的研究和注释著作难以胜数,其中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精选读本,最有学习研究的价值。
朱熹在汉唐训诂注疏之经学的基础上,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朱熹之经学,周予同、邱汉生、蔡方鹿、林庆彰、姜广辉等有全面深刻的论述。①朱熹的经学,包括了经学的各个领域,诸如“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学等。这里,主要论述朱熹的“四书”学。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之名由此始。周予同说:
按《论语》,汉文帝时曾立博士,《汉书·艺文志》附于六经之末。《孟子》本战国儒家之一支派;赵岐《孟子题词》虽谓文帝时亦尝立博士,然其说不可甚信;《汉志》以来,向列于子部儒家,与《荀子》并称《孟》、《荀》。至于《大学》与《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二篇;《汉志》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中庸》别行,古已有之;唯《大学》一篇,向附《戴记》,李唐以前,未有别行之本。自宋儒性理之学兴,于是开《孟子》以配《论语》,出《学》、《庸》以别《戴记》。……朱熹承小程之学,以《四书》为其哲学上之论据,于是殚精悉力,从事训释。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复撰《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而其他《论孟精义》、《论孟要义》、《学庸详说》等之初稿尚不计焉。②
朱熹积40年之功,对“四书”精加注释,将其《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刻,成《四书章句集注》。用“四书”取代传统的“六经”,用“四书”义理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朱熹的“四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个里程碑。
朱熹的“四书”学以明道为宗旨,因此他以理学的逻辑顺序排列“四书”次序。对此,黄榦有所概括: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合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对此,朱熹提出如下的学研“四书”的次序。他说: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②
在朱熹看,《大学》不仅是“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之先务。这是因为,《大学》系统地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践履次第,是修身治国的纲领。通过治《大学》,打下根基,才能真正明白儒学。这里,一是先难后易,遵循渐进的为学原则;二是依据儒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更掌握理学的内容实质。
汉唐儒者大多用对“六经”训诂注疏的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而宋学学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主要是通过治“四书”来阐发义理和新儒学的天理论,故“六经”和“四书”分别为汉学学者和宋学学者所看重,而成为各自治经学所主要依据的经典。这在朱熹提出“四书”重于“六经”思想后的南宋更是如此。
朱熹在二程等思想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理学理论为标准,倾其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用重义理及天理论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据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引用历代注家50多处,其中主要是理学家的注疏,引二程言论239处,居于首位,其次是二程的弟子及后学,张载等理学家的言论也有所引,再就是苏轼、王安石、吴棫等宋学学者的材料。至于汉学学者的言论,朱熹虽也加以征引,如郑玄、马融、赵岐等,但条数则较少。由此可见朱熹对理学、宋学、汉学的远近亲疏的认同程度。
朱熹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因为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①
这即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其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其本义皆非为阐发义理而作。因此,朱熹指出,如果要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论语》、《孟子》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论语》等“四书”的位置。他强调:“《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
朱熹认为,儒家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之中,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圣人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理学思想;还是重训诂,注重对“六经”的注疏,这是朱熹经学与汉唐经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区别的标帜。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而朱熹在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此小异反映出了朱熹经学的特点,以及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亦是对汉唐经学的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发展。
朱熹之治“四书”,遵循其先后之序,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史学、哲学等重要内容,最终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论证。③
三 史学
基于上述,朱熹的史学跟其经学一样,主要的是通过阐述儒家典籍,根据儒家典籍中的观点和材料,评价、编纂历史。综观朱熹的主要史学著述,诸如《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保存于《朱子文集》中的历史人物年谱、行状、传记和其他史学专题论文,以及《朱子语类》中的有关言论等,其历史学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正统论问题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循环的五行相生相胜的君权神授的历史观,后来班固明确宣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将刘汉说成是上承三代的正统王朝。
朱熹在继三代为正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正统论。朱熹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大权是否归一,是正统的首要标准。据此,宋前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6个统一王朝称得上正统,其他难于归正统之列。对此,有两种情况。朱熹说:
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②
这是讲正统之始。至于正统之余,是指正统王朝分裂,或偏安一地,如东晋、蜀汉。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便是无正统可言,称之为僭国或篡贼。
朱熹指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统”③。朱熹处于赵宋偏安江南,为蜀汉争正统实为赵宋争正统,以正名分,用伦理纲常来评判历史。
朱熹正统论的内在根据,是“以经为本”。他反复强调:
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④
示谕学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时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诚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学业,虽未能深解义理,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时文,为目前苟简之计也。①
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此间来学者少,亦欲放(仿)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经,或《论》、《孟》已无余力矣。所抄切己处,便中得数段见寄,幸甚。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②
在朱熹看来,史著与经书等都是为了辨验是非、阐明义理;史著文词多寡、辞采优劣不是史著好坏标准,贯穿义理与否才是标准;史臣著史的职责(即史著的作用)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对“苏黄门作《古史序篇》……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认为于世有补而大加褒扬。③
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凶吉存亡、为戒为法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④以此来讽劝帝王读经看史,辨析义理,改邪归正,励精图治。这种劝善惩恶之意,折射出朱熹要求编纂史著时要体现这一内容,而使史著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二)秉笔直书
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也。”⑤这里的义,是指思想意识、学术观点,即古人所说的史德。史学家著述,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主观的好恶去歪曲历史。义(史德)是治史的精神,再加事(掌握历史事实)、文(写作能力、文采),就能撰写出好的史书来。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把历史著述看成是实录。有史德才能实录,就是善恶皆不隐的直书。班固在评价司马迁《史记》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⑥
朱熹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在朱熹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⑦,否则难以垂训万世。只有像孔子那样据实著史,才是可以为鉴为戒的。因此,朱熹甚有感触地评论东晋陶侃之事,其引吴澥所著《辩论》曰:
庾氏世总朝权,其志一逞,遂从而诬谤之耳。秉史笔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见曲出,乃所以证成其罪也。……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必渝以闺房之事,以其难明故也。今《晋书》欲诬士行,而乃以梦寐之祥,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①
朱熹赞同吴澥的这种史观。朱熹的这种著史不为权贵所左右的观点,据实而书,是与后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的“史德”完全符合的。②
(三)主要史著
《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书撰编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39岁。其基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说:
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栝,以就此编。……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③
参与是书编撰的有门人赵师渊等人。怕自己与参与编撰的门人离开其动机与目的,朱子特地亲手制订了19章137条的详细“凡例”,其大要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法《春秋》、除史弊。在这里明正统是根本,因为从义理的角度看,如果法统不正,也就失去了是非得失的标准。朱熹把这部史著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事实“会归于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慨然有感于斯”。
今天读《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19章137条,订得是那么具体,什么事该书,什么事不该书,什么事又该怎么书,这实际上是在一字定褒贬,并非直载当时之事。《资治通鉴纲目》不追求史实是否真正可靠,而是在用理学家的义理观来评估历史。
《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自赵普至苏洵等55位名臣,附5人)、《三朝名臣言行录》14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自韩琦至陈师道等44位名臣)。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说:
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摄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①
据此,看出是从义理的角度上衡量的。书中所选的近百名名臣,都是关系宋朝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的言行是与宋朝的政治盛衰息息相关的。所以读这部书既能知道名臣们的为人和政治态度,又能通过他们的言行看出宋朝政治的盛衰。
《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人系事,荟萃群言,又注明出处,条理清楚,叙次明白。这种编纂方法后世有仿效与接续,出现明沈应奎编的《名臣言行录新编》、编者不详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明徐咸编的《近代名臣言行录》等。这类书虽然还构不成一个系列,但说明朱熹在这方面是有开创性的。
《伊洛渊源录》14卷 此书是记录二程及其弟子的学术史。编写始终都与吕祖谦进行商量。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曰: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首末。因书士龙(按指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渊源》、《外书》,皆如所喻。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②
编纂是书的动机与目的是说明圣贤之用,义理之正,标明二程思想为理学正宗,着重探讨二程以前诸儒对二程学说形成的影响源远流长。书中除了详细记述二程及程门弟子中比较著名学者的言行以外,对程门弟子言行无大影响的亦具录姓名,以志当年程门学说之盛。
《伊洛渊源录》在编纂体例上首创以事状、遗事与言论合编的形式,使读者既能从中了解当时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也能了解到他们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种编纂体例,既影响了后来元代编修《宋史》时将“道学”与“儒林”分传,启发了后来谢铎、薛应旗、朱衡、张伯行等也分别编纂《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道学源委》等书,也影响了后来周汝登编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编的《理学宗传》及黄宗羲编的《明儒学案》等书。
中华民族历代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通过汉字这一传播媒介充分地记录表达出来,形成浩如烟海的典籍。对这些典籍,前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史是指以反映历代国家历史、典章制度、土地等的文献;子是指历代学者的诗、文的汇集;集是指类书、丛书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典籍的汇集。这些古代典籍,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结晶。
上述学科,过去集中于文、史、哲(包括宗教)三个最为重要的学科。古人治学不细,把诸学科都纳入经学的范围内。经、史、子、集分类法是由经学衍化出的。清代学者又提出史学最具有综合性,认为它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所有学术领域,因为每个学科都需要首先考察历史发展,而且中国古代典籍都可以运用于历史的研究中。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得到著名学者龚自珍、章炳麟等的赞同。①他们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朝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贤们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造出来的。
朱熹也是把经学、史学,联系在一起的,提出“穷经观史以求义理”、“多读经史,博通古今”、“经史阁”等,认为“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时之用矣”②。经学、史学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
朱熹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其理论的提出,几乎都与他的经学、史学分不开,他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都蕴含有历史学。当时没有学科划分,朱熹结合时代的需要,通过对诸经的训解阐释而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其哲学等思想,都是后人根据现代学科分类及学科名词,通过研究朱熹经学、史学而提出来的。《朱子语类》卷一四至九二都是直接讲朱熹的经学、史学的,占整个《朱子语类》的一大半。其余的内容也与经学、史学有密切联系。朱熹的其他著作,大多是对儒家经书、史学的注释和阐发,如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四书或问》、《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古今家祭礼》、《仪礼经传通解》、《孝经刊误》等。《朱子文集》中的诸多书信答问,大量的是与当时的众多学者讨论经学、史学的问题,而《文集》中的杂著,大部分内容也是对经学、史学的论述。这说明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主。他是在对经书的阐述基础上发挥其历史观。
二经学
经学是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战国时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至汉代,经学大盛。然经学之名则见于《汉书》:兒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③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现实社会服务。离开了儒学,便无经学。而离开了经学,也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既不能把经学与儒学混为一谈,亦不可把二者截然分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先秦儒家经典主要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有目无书,说法不一,汉代人删去而增进《孝》《论语》,合称七经。唐代人又扩至九经或十二经:把《礼》析为《周礼》、《仪礼》、《礼记》,再增进《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尔雅》。宋代人增进《孟子》,总称“十三经”。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经书的选集。历代对经书的研究和注释著作难以胜数,其中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精选读本,最有学习研究的价值。
朱熹在汉唐训诂注疏之经学的基础上,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朱熹之经学,周予同、邱汉生、蔡方鹿、林庆彰、姜广辉等有全面深刻的论述。①朱熹的经学,包括了经学的各个领域,诸如“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学等。这里,主要论述朱熹的“四书”学。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之名由此始。周予同说:
按《论语》,汉文帝时曾立博士,《汉书·艺文志》附于六经之末。《孟子》本战国儒家之一支派;赵岐《孟子题词》虽谓文帝时亦尝立博士,然其说不可甚信;《汉志》以来,向列于子部儒家,与《荀子》并称《孟》、《荀》。至于《大学》与《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二篇;《汉志》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中庸》别行,古已有之;唯《大学》一篇,向附《戴记》,李唐以前,未有别行之本。自宋儒性理之学兴,于是开《孟子》以配《论语》,出《学》、《庸》以别《戴记》。……朱熹承小程之学,以《四书》为其哲学上之论据,于是殚精悉力,从事训释。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复撰《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而其他《论孟精义》、《论孟要义》、《学庸详说》等之初稿尚不计焉。②
朱熹积40年之功,对“四书”精加注释,将其《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刻,成《四书章句集注》。用“四书”取代传统的“六经”,用“四书”义理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朱熹的“四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个里程碑。
朱熹的“四书”学以明道为宗旨,因此他以理学的逻辑顺序排列“四书”次序。对此,黄榦有所概括: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合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对此,朱熹提出如下的学研“四书”的次序。他说: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②
在朱熹看,《大学》不仅是“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之先务。这是因为,《大学》系统地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践履次第,是修身治国的纲领。通过治《大学》,打下根基,才能真正明白儒学。这里,一是先难后易,遵循渐进的为学原则;二是依据儒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更掌握理学的内容实质。
汉唐儒者大多用对“六经”训诂注疏的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而宋学学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主要是通过治“四书”来阐发义理和新儒学的天理论,故“六经”和“四书”分别为汉学学者和宋学学者所看重,而成为各自治经学所主要依据的经典。这在朱熹提出“四书”重于“六经”思想后的南宋更是如此。
朱熹在二程等思想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理学理论为标准,倾其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用重义理及天理论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据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引用历代注家50多处,其中主要是理学家的注疏,引二程言论239处,居于首位,其次是二程的弟子及后学,张载等理学家的言论也有所引,再就是苏轼、王安石、吴棫等宋学学者的材料。至于汉学学者的言论,朱熹虽也加以征引,如郑玄、马融、赵岐等,但条数则较少。由此可见朱熹对理学、宋学、汉学的远近亲疏的认同程度。
朱熹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因为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①
这即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其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其本义皆非为阐发义理而作。因此,朱熹指出,如果要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论语》、《孟子》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论语》等“四书”的位置。他强调:“《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
朱熹认为,儒家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之中,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圣人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理学思想;还是重训诂,注重对“六经”的注疏,这是朱熹经学与汉唐经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区别的标帜。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而朱熹在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此小异反映出了朱熹经学的特点,以及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亦是对汉唐经学的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发展。
朱熹之治“四书”,遵循其先后之序,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史学、哲学等重要内容,最终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论证。③
三 史学
基于上述,朱熹的史学跟其经学一样,主要的是通过阐述儒家典籍,根据儒家典籍中的观点和材料,评价、编纂历史。综观朱熹的主要史学著述,诸如《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保存于《朱子文集》中的历史人物年谱、行状、传记和其他史学专题论文,以及《朱子语类》中的有关言论等,其历史学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正统论问题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循环的五行相生相胜的君权神授的历史观,后来班固明确宣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将刘汉说成是上承三代的正统王朝。
朱熹在继三代为正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正统论。朱熹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大权是否归一,是正统的首要标准。据此,宋前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6个统一王朝称得上正统,其他难于归正统之列。对此,有两种情况。朱熹说:
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②
这是讲正统之始。至于正统之余,是指正统王朝分裂,或偏安一地,如东晋、蜀汉。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便是无正统可言,称之为僭国或篡贼。
朱熹指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统”③。朱熹处于赵宋偏安江南,为蜀汉争正统实为赵宋争正统,以正名分,用伦理纲常来评判历史。
朱熹正统论的内在根据,是“以经为本”。他反复强调:
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④
示谕学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时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诚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学业,虽未能深解义理,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时文,为目前苟简之计也。①
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此间来学者少,亦欲放(仿)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经,或《论》、《孟》已无余力矣。所抄切己处,便中得数段见寄,幸甚。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②
在朱熹看来,史著与经书等都是为了辨验是非、阐明义理;史著文词多寡、辞采优劣不是史著好坏标准,贯穿义理与否才是标准;史臣著史的职责(即史著的作用)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对“苏黄门作《古史序篇》……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认为于世有补而大加褒扬。③
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凶吉存亡、为戒为法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④以此来讽劝帝王读经看史,辨析义理,改邪归正,励精图治。这种劝善惩恶之意,折射出朱熹要求编纂史著时要体现这一内容,而使史著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二)秉笔直书
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也。”⑤这里的义,是指思想意识、学术观点,即古人所说的史德。史学家著述,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主观的好恶去歪曲历史。义(史德)是治史的精神,再加事(掌握历史事实)、文(写作能力、文采),就能撰写出好的史书来。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把历史著述看成是实录。有史德才能实录,就是善恶皆不隐的直书。班固在评价司马迁《史记》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⑥
朱熹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在朱熹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⑦,否则难以垂训万世。只有像孔子那样据实著史,才是可以为鉴为戒的。因此,朱熹甚有感触地评论东晋陶侃之事,其引吴澥所著《辩论》曰:
庾氏世总朝权,其志一逞,遂从而诬谤之耳。秉史笔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见曲出,乃所以证成其罪也。……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必渝以闺房之事,以其难明故也。今《晋书》欲诬士行,而乃以梦寐之祥,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①
朱熹赞同吴澥的这种史观。朱熹的这种著史不为权贵所左右的观点,据实而书,是与后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的“史德”完全符合的。②
(三)主要史著
《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书撰编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39岁。其基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说:
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栝,以就此编。……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③
参与是书编撰的有门人赵师渊等人。怕自己与参与编撰的门人离开其动机与目的,朱子特地亲手制订了19章137条的详细“凡例”,其大要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法《春秋》、除史弊。在这里明正统是根本,因为从义理的角度看,如果法统不正,也就失去了是非得失的标准。朱熹把这部史著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事实“会归于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慨然有感于斯”。
今天读《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19章137条,订得是那么具体,什么事该书,什么事不该书,什么事又该怎么书,这实际上是在一字定褒贬,并非直载当时之事。《资治通鉴纲目》不追求史实是否真正可靠,而是在用理学家的义理观来评估历史。
《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自赵普至苏洵等55位名臣,附5人)、《三朝名臣言行录》14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自韩琦至陈师道等44位名臣)。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说:
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摄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①
据此,看出是从义理的角度上衡量的。书中所选的近百名名臣,都是关系宋朝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的言行是与宋朝的政治盛衰息息相关的。所以读这部书既能知道名臣们的为人和政治态度,又能通过他们的言行看出宋朝政治的盛衰。
《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人系事,荟萃群言,又注明出处,条理清楚,叙次明白。这种编纂方法后世有仿效与接续,出现明沈应奎编的《名臣言行录新编》、编者不详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明徐咸编的《近代名臣言行录》等。这类书虽然还构不成一个系列,但说明朱熹在这方面是有开创性的。
《伊洛渊源录》14卷 此书是记录二程及其弟子的学术史。编写始终都与吕祖谦进行商量。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曰: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首末。因书士龙(按指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渊源》、《外书》,皆如所喻。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②
编纂是书的动机与目的是说明圣贤之用,义理之正,标明二程思想为理学正宗,着重探讨二程以前诸儒对二程学说形成的影响源远流长。书中除了详细记述二程及程门弟子中比较著名学者的言行以外,对程门弟子言行无大影响的亦具录姓名,以志当年程门学说之盛。
《伊洛渊源录》在编纂体例上首创以事状、遗事与言论合编的形式,使读者既能从中了解当时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也能了解到他们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种编纂体例,既影响了后来元代编修《宋史》时将“道学”与“儒林”分传,启发了后来谢铎、薛应旗、朱衡、张伯行等也分别编纂《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道学源委》等书,也影响了后来周汝登编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编的《理学宗传》及黄宗羲编的《明儒学案》等书。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