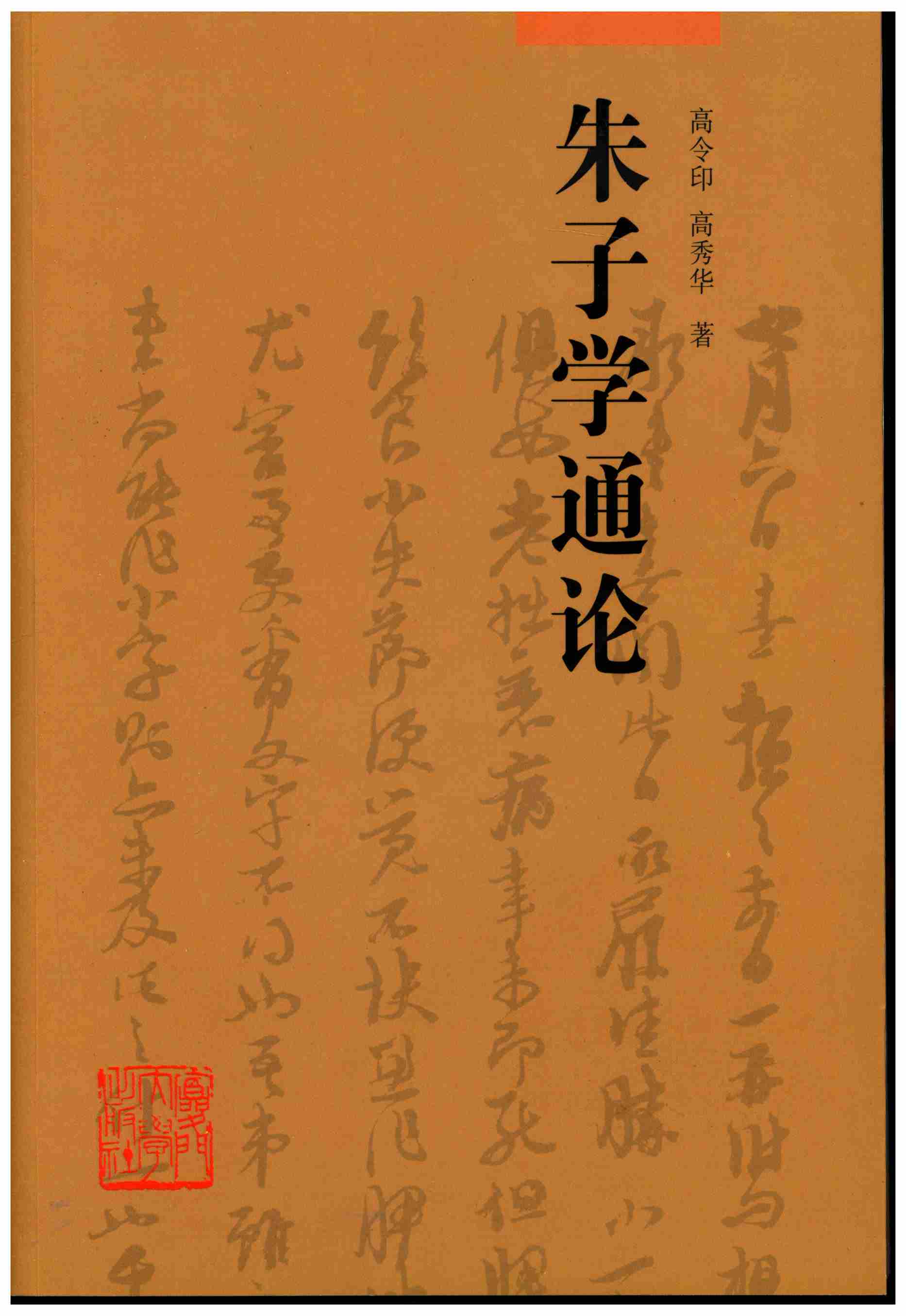内容
一 无极与太极
无极、太极是朱子学的重要范畴,是其世界观的出发点,并涉及多方面的关系,首先加以说明。
朱熹把“极”理解为“至”,即“终”、“穷”、“尽”、“竟”之义。朱熹反复讲了这个问题。朱熹说:
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①
他还谓,“极是极至无余之谓。”“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极之义。”枢极指北辰之为天极。“极,尽也。先生指前面香桌,四边尽处是极,所以谓之四极。四边视中央,中央即是极也。”但是,“中不可解做极。极无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极之所为。四向所标准,故因以为中。如屋极亦只在中,为四向所准。”如北极,如宸极,皆然。若只是说中,那就不是极之涵义。②
朱熹认为,太极,因其极至,故谓之太极。上引《语类》中也反复讲了太极的问题。他认为,太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没有去处。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都是没有去处。自外面推进去,到极尽处,没有去处,所以叫做太极。由此,朱熹便得出太极为天地万物之根柢、大源,天地万物之所由出。他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著夫无声臭之妙也。”①
朱熹进一步指出,“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又一图之纲领,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要根柢也。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者哉?近世读者不足以识此,而或妄议之,既以为先生病,史氏之传先生者,乃增其语曰‘自无极为太极’,则又无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尝欲援故相苏公请刊国史‘草头木脚’之比,以证其失。”②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并非无极之后另生太极,太极之上先有无极。无极是形容太极的,即无形而有理之意。他在《答陆子静书》第五书中有曰:
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③
朱熹注《太极图说》之“无极而太极”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原注:是解‘无极’二字),而实造化之极枢,品汇之根柢也(原注:是解‘太极’二字)。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原注:‘有无合一之谓道’)。”④门人杨方对朱熹之注提出异议。朱熹解释曰:
然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气)五(行);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万物,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图之纲领,《大易》之遗意,与老子所谓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矣。⑤
朱熹所谓无极,是讲无之至,而至无之中,乃至有存。无极无声无臭。非太极之外别有无极。太极无极无次序,无先后,无积渐。亦不可将无极便做太极。
周子恐人以太极为一物,故说“无极而太极”,只是无形而有理之意。
朱熹说“无极而太极”,还跟理联系在一起。如其曰:
盖其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①
朱熹门人大都发扬朱熹的这种说法。《北溪语录》录陈淳的有关说法。陈淳认为,“太极只是理,理太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自其冲漠无朕,此浑沦无极之妙也。”真德秀在《论语集篇》中说:
所谓无极而太极者,岂太极之上别有所谓无极哉,特不过谓无形无象而至理存焉耳。盖极者,至极之理也。穷天下之物可尊可贵,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极也。世之人以北辰为天极,屋脊为屋极,此皆有形可见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极为一物,故以无极二者加于其上,犹言本无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阴阳而下丽乎形气矣。阴阳未动之先只是此理,岂有物之可名邪?②
此引真德秀讲的太极与阴阳的关系,全是朱熹之意。朱熹认为,太极在阴阳之中,非在阴阳之外;阴阳亦在太极之中。“所谓太极者,便只是在阴阳里。所谓阴阳者,便只是在太极里。而今人说阴阳上面别有一个,无形无影底物是太极,非也。”但是,太极与阴阳却不能等同,把它们混而为一。阴阳动静,动静皆太极状态,而动静却非太极。朱熹说:
不是(太极)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③
在朱熹看来,阴静是太极之本,而阴静却由阳动而生。“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譬如鼻息,无时不嘘,无时不吸。吸尽则生嘘。理自如此。”④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是动后方生阳,盖才动便属阳,才静便属阴。动而生阳,其初本是静。静之上又须动。不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截然焉两段,先有此而后有彼。只是太极之动便是阳,
静便是阴。方其动时,则不见阴。方其静时,则不见阳。这就是动而生阳的含义。这即是程颐在《经说》中所说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意。
对于朱熹的太极动静,蔡沉从形而上下去解释。他说:
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①
这是蔡沉从抽象与具体上论说太极动静之理的。
黄榦再进一步把太极阴阳与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有太极分阴分阳,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黄榦在《复杨仁志》中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尝在一之先?……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见。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往而非二也。如是则二者,道之体也,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不二哉!……天下之物无独必有二。若只生一,则是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何尝在一之先,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生两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
黄榦这里是批判老子的观点。他认为,“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老氏之所谓道,非吾儒之所谓道也。”②
朱熹不同意用体用理解静动。他认为,太极本来就是涵有动静之理的,却不能以静动分体用。这是因为,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摇动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③朱熹的门人大都沿着朱熹的这个说法发挥。
二 理与气
朱熹在讲太极时,已谓“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理是天地万物之道理。天地万物,则必各有所然之故和其所以当然之则。陈淳说:“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则是准则,法则。有个确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当合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些不及些,便是则。”④真
德秀在《格物致知之要一》中说:
理未尝离于物之中,知此则知有物有则之说矣!盖盈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视、耳之听,物也;视之明、听之聪,乃则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乃则也。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谓规、矩、准、绳、衡为五则者,以其方圆、平直、轻重,皆天然一家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为之,但循其则尔。如视本明,视而不明,其失其则也。①
这就是说,理指文理、条理,即事物之规则,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规律。
朱熹反复强调,理是实实在在的,并非虚无。这是因为,理与气不离,理在气中,二者相辅而行。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就在气之中。朱熹曰: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②
气不能无理,因凡人物必须有其所以然。理不能无气,因理不是空虚之物。理非别为一物,理存在于物之中。无是气,则是理无挂搭处。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如是浑然一体,非两物并存。朱熹在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曰:“理附搭于气而行。”③所谓理附搭于气,并非指气为主,理为宾,而是理气不离,气亦附理,无主客之分。有门人问动静者,朱子答说: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④
此处把太极、理、气三者的关系都讲清楚了。
陈淳以浑沦释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所谓浑沦,就是像云雾一样茫茫无限。此论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其实,理不外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有主之,曰理是也。然理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
指出个理不离于气而为言耳。”①陈淳强调,虽谓以理为主,但是理在气中,理是通过气而体现出来的。陈淳有把理气合一之倾向。如果说在朱熹那里是把气作为理生物的中间环节,而在陈淳这里则有气直接产生物的气息,具有张载气论的因素。
理气不离不杂并没有否认理先气后。这在朱子学本体论体系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在《朱子语类》答问和《朱子文集》书札中讨论很多。《中庸章句》、《大学或问》、《易学启蒙》亦涉及之。朱熹论太极时曰:“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②在论天地时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③在论人物时曰:“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④在论性时曰:“先有个天理,却有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⑤在论动静时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⑥此处非指理之本身有动有静,而是指如无动静之理,则动静无由施行。在论感应时曰:“未有事物之时,此理已具。少间应处,只是理。……未应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这个道理。”⑦
理先气后并不与理气不离不杂相矛盾,它们是一致的。朱熹所强调的理先气后,是从逻辑上讲的。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说: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⑧
此处先言理在气先,随谓理气不离。朱熹在《答刘叔文》第一书中说: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①
这里明确讲逻辑推论。在朱熹看来,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是理在先气在后。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在《朱子语类》讲到这个问题时,冯友兰于此言下案语曰:“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若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②朱熹理气不离不杂与理先气后之说,具有非常深刻的逻辑学的意义。
不仅如此,在理气关系上,朱熹还强调理生气,有是理然后生是气。此“生”非生“子”之生,而是“生事”、“生心”之“生”,含有本原之意,亦有存在所由之意,即上面所说的必然之性,是指“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论运行,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会他不得。如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若论本原,则可谓理强气弱,因理是气之必然性。在此意义上,理是气之主宰。其门人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者否?”朱熹答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③此主宰非有意之主宰,而是如程颐所谓“天地无心而成化”④之主宰,亦即理决定气之種種存在与性质之主宰。
对于理气关系,蔡沉以其数理论加以解释。其《洪范皇极·内篇》中反复强调,“有理斯有气,气著而理隐。有气斯有形,形著而气隐。人知形之数,而不知气之数;人知气之数,而不知理之数。知理之数,则几矣。动静可求其端,阴阳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万物可求其纪;鬼神知其所幽,礼乐知其所著。生知所来,死知所去。《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在蔡沉看来,理之数是“几”,即包含了理生气、气生形的动因。他说:
有理斯有气,有气斯有形,形生气化而生生之理无穷焉。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赜。复土之陵,积水之泽,草木虫鱼,孰形孰色。无极之真,二五之数,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测其神,莫知其能。⑤
蔡沉所表达的朱子学本体论之太极、理、气诸范畴与朱熹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加了个“数”。蔡沉的世界图式论以数作为基础,始终贯串着数之关系。
天即理,是朱熹理学的本色。“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①
朱熹据《易·系辞传》之“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得出“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②
既然天地以生物为心,那么人、物得之必以为心。一个天地之心是指大宇宙,一人一物之心是指小宇宙。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人心之理和万物之理都是由天理分殊出来的。
朱熹据当时北宋理学家的理气观点,又参照释、道的有关说法,便明确了“理一分殊”之意。朱熹说:
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里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圣贤之学,非老氏之比。老氏说“通于一万事毕”,其他都不说。少间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③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如排数器水相似:这盂也是这样水,那盂也是这样水,各个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然打破放里,却也只是个水。此所以可以推而无不通也。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④
此“月印万川”,亦即佛家所常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就是说,人心之理与万物之理都是由天理分殊出来的。显然,朱熹的理一分殊论是吸取了释、道之合理思想的。
朱熹给传统的天人合一赋予理一分殊的新意,找到了天是如何衍化出人、物的,使中国人的世界观严密完整,更富有特色。朱熹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创见。他说:熹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则见“仁”字与“心”字浑然一体之中,自有分别,毫厘有辨之际,却不破碎,恐非如来教所疑也。①
此“臆见”是由释氏之“月印万川”启发出来的。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仁,仁则生。仁为众善之首,仁自然又生出义礼智等美德。
朱熹的理一分殊论,真德秀用体用一元来解释。他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但是皆为根本理之体现。根本的理是本体,每个事物所具有的理是万殊,都是根本理的作用和运用,而且是根本理的缩影。根本的理和万殊的理都是道,因此是体用一元的。这就是真德秀所说的“至诚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殊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真德秀又说:
天下之理一,而分则殊。凡生于天壤之间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气者也,是之谓理一。然亲者吾之同体,民者吾之同类,而物则异类矣,是之谓分殊。以其理一,故仁爱之仁无不遍;以其分殊,故仁爱之施则有差。以亲亲之道施于民,则亲疏无以异矣,是乃薄其亲;以仁民之道施于物,则贵贱无以异矣,是乃薄其民。故于亲见则亲之,于民则仁之,而于物则爱之。合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异于杨、墨也。②
在真德秀的理一分殊论中,包含了一般与个别、一与多的辩证法因素。但是,真德秀有时认为,万殊分别完美无缺地体现了一理,有把一般与个别、一与多等同之嫌,而且他把理一分殊主要分析道德伦理关系,其辩证法是不彻底的。
朱子学学者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由原先孔子的伦理内涵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儒学建立起完备精密的形上学系统。他们用“理一”统摄“万殊”,把儒家的本体论、人生观、知行观糅合成一个整体。
三心与性情
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提出理一而万殊,把一理与万殊联系起来。那么,一理与万殊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朱子学家们的心性论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他们依据《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即人、物之性是由天理所赋予的,心是
神明之舍、一身之主宰,即心是认识和道德之主体。作为认识的主体,心要和理、事物发生关系。朱熹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①心作为道德主体,又有道德与非道德意识,便有道心与人心的问题。
朱熹的心性论,更多地得之于释、道之说。对此,朱熹有反复的论说:
(朱熹)因举佛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曰:“朴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看他是怎么样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为他挥下也。此是法眼禅师下一脉宗旨如此。今之禅家皆破其说,以为有理路,落窠臼,有碍正当知见。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之不落窠臼不坠理路。妙喜之说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转不如此说时。②
此是说明儒、释之心性说的相似处。朱熹之心性言论,大都似慧能《坛经》等说法,如慧能在《坛经》中谓“万法在诸人性中”、“自心见性”,③朱熹则谓“若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④、“性之理包在心内,到发时却是性底出来”⑤,等等,比比皆是。朱熹说:
佛学其初只说空,后来说动静,支蔓既甚,达摩遂脱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静见理。此说一行,前面许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难为抗衡了。今日释氏其盛极矣。但程先生所谓“攻之者,执理反出其下”。吾儒执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胜也。⑥
朱熹把《坛经》等释、道书中的心性、心体、心量、明心见性、心静见理等由“虚无”放置于“实有”上,反其意而用之,成为自家的珍品,然后“执理”再与其对抗,自然就显得对方空洞贫乏无力了。
在朱熹看来,儒与释、道之学在心性问题上貌同而神异,不同的只是内涵。要在释、道心性的形式中填入儒家的内容。此在《朱子语类》中有反复的论说。
他认为,“吾以心与理为一,彼(释、道)以心与理为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虽说心与理一,无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是见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学》所以贵格物也。”基于这种认识,朱熹便广泛地论及释、道之心性说,录己之所需要者。据《朱子语类》记载:
问释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这性,他说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便是此性。如口会说话,说话底是谁?目能视,视底是谁?耳能听,听底是谁?便是这个。其言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他说得也好。又举《楞严经》波斯国王见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禅家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只要你见得,言下便悟,做处便彻,见得无不是此性。也说“存心养性”,养得来光明寂照,无所不遍,无所不通。唐张拙诗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云云。又曰:“实际理地不受一廛,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他个本自说得是,所养者也是;只是差处便在这里。吾儒所养者是仁义礼智,他所养者只是视听言动。……只认得那人心,无所谓道心,无所谓仁义礼智。……他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云云。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至神鬼神仙士农工商技艺,都在他性中。他说得来极阔,只是其实行不得。①
朱熹认为,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这是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以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此只是源头处错了。这就是说,释者人心之说有可取之处。人之道德理性亦含于心中,当心(心官、报身)起用时,心不仅有自然之思之妙用,且能思其所当思当行,有知是非之良知良能。理学家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性即天理,无有不善。而理与气便形成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同时受理与气的作用,因气有清浊、偏正,所以气质之性是天理与人欲的综合。
上面是讲朱熹论儒释心性之不同和相互关系。下面具体说明朱子学的心性论。先看其心论。朱熹谓,“有知觉谓之心。”②这是讲心对外物有感知,能对外物有反映。朱熹说:“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①是讲心有思虑功能。朱熹又说:“心,主宰之谓也。”②此主宰是指主于一身和主于万事,前者说的主宰是感觉器官,后者说的是心具有能动作用,使事物能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对此,真德秀在《天性人心之善》中说得更明确,认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心其能穷天理而无不立者也。”③这是讲心的认知能力。
上面讲的是主观意念之心,是人心。此外,还有天地之心。人心是天地之心的一部分。所谓天地之心,是指天地生物之心,是宇宙万物和包括人心在内的天下之心存在的总根源,即万物产生的本原。天地之心表现在人方面则为人心,人心便是人得天地之心而成其为己心。朱熹说:
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贯。④
这是说,天地之心和人心贯串着一条仁的脉络。所谓“心德”,即仁义礼智心之四德,由仁统帅之。
上面讲的人心,其一个含义是有知觉。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心,按其知觉的来源和内容便可有两种不同的心。朱熹说:
或问“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著。微,亦微妙之义。⑤
道心是指以义理为人内容的心,仁义礼智为善,道心亦为善。而人心则指的是原于耳目之欲的心。人生有欲,饥食渴饮,虽圣人不能无心,故人心不是全不好的,可为善亦可为不善。朱熹认为,人是形气和性命结合的产物,人生有欲,这是人不可避免的;而心中有理,这是上天所赋予的。所以,人心与道心是人人所有之的。朱熹说:
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够无人欲;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够无道心。①
道心是以义理为内容的,原于性命之正,道心至善;人心是以耳目之欲为内容的,生于形气之私,人心有善有恶。人心与道心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是人之一心的两种表现。
对此,陈淳有更深入的综合说明。他说:
心者,一心之主宰也。人之四肢运动,手持脚履,与夫饥思食、渴思饮、夏思葛、冬思裘,皆是其心为之主宰。今如心羔的人,只是此心为邪气所乘,内无主宰,所以日用间饮食动作皆失其常度,与常人异。理义都丧了,只空有个气,仅往来于脉息之间,未绝而已。大抵人得天地之理为之性,得天地之气为之体,合理与气方成这个心,有个虚灵知觉,便是心所以为主宰处。然这个虚灵知觉,有发于理者,有发于气者,各有不同。②
在陈淳看来,心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心能认识客体。如果认识正确,就会有正确的动机和行为,它就是道心;反之,如果认识错误,就会产生不正确的动机和行为,它就是人心。陈淳又说:
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其所以为虚灵知觉,由形气而发者,以形气为主,而谓之人心;由义理而发者,而谓之道心。若目能视,耳能听,口能言,四肢能动,饥思食、渴思饮、冬思裘、夏思葛等类,其所发皆本于形气之私,而人心之谓也。非礼勿视,而视必思明;非礼勿听,而听必思聪;非礼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礼勿动,而动必思义;食必有礼……饮必有节……寒不敢裘,暑毋褰裳,其所发皆源于义理之正,而道心之谓也。③
陈淳认为,性是天理,它是至善的。从性流出来的是道心,从物欲触发出来的是人心。道心是全善的,而人心则是有善有恶。“从理上发出来的”,就是正确的行为和动机,亦即是仁、义、礼、智之心,就是道心。“从形气上发出的”,就是有不正确的行为和动机,亦即饥思食、渴思饮之类的心,就是人心;道心对于饮食,要从理上考虑当不当饮食,如不食嗟来之食。在朱熹那里,注重在善恶上解释人心、道心;而陈淳则是注重在出发点上解释人心、道心,以感官的天然倾向为人心,以伦理的天然倾向为道心,更注重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因此,陈淳发展了朱熹关于人心、道心的思想。在陈淳看来,出于人自私目的的是人心,出于义理目的是道心。人心总是自私的,它是臬危兀危不安的;道心总难
免遭受人心的蒙蔽,不易充分显露出来。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在于努力使道心处于支配的地位,而使人心服从道心的支配。
上面讲的是心。再看看他们对性的认识。朱熹在《玉山讲义》中深刻地叙述了性的问题。他说: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凡此四者(仁义礼智)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慾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应正谓此也。……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①
《玉山讲义》是朱熹晚年成熟著述,全面概括地论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是治朱子学者必读之书。人之情是与性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认为,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性为静、未发、体;而情的内涵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以及喜、怒、哀、乐等,情为动、已发、用。朱熹在《答胡伯逢》第四书中说:
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之言,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己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性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有改者也。②
未发是指仁义礼智之性未表现出来的状态,即思虑未萌时心之状态;已发是指思虑已萌时心之状态。朱熹强调,善贯串于未发、已发两端,即情发而中节,符合性的原则,即善的表现。
朱熹是从心兼体用上理解心兼已发未发的。他认为,由于心统情性,心有体用,故心跨已发未发两头。这是从逻辑上推论。朱熹在《答林泽之》第六书中说:
未发只是思虑事物之未接时,于此便可见性之体段,故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也;发而中节,是思虑事物已交之际,皆得其理,故可谓之和,而不可谓之心。心则通贯乎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①
未发已发是心体流行一静一动两个不同的阶段。可见,心之未发与心之体、心之静相联系;心之已发与心之用、心之动相沟通。心具有未发、已发两种状态,即指心兼未发、已发。
需要指出,心之未发时可见性之体,性具于心,但心不等同于性;心之已发时可见情之著,情通于心,但心不等同于情。虽然心贯通于未发之性和已发之情,但心与性、情有各自不同的确切涵义和规定性,彼此不能相混。朱熹在《已发未发说》中说:
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此之时,敬以持之,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则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此日用之际,本领工夫,其曰“却于已发之处观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动,而致扩充之功也。一不中,非性之本然,而心道或几乎息矣。故程子于此,每以“敬而无失”为言。②
此指出心之未发可谓之中,然不可谓之性。心之已发,谓之和,情为心之用,但情也并不等同于心。
朱熹心兼已发未发,即心贯通于已发未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最后确立的过程。在已发未发问题上,开始时朱熹受程颐及胡宏思想的影响,持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这与他自己后来形成的心兼已发未发的思想大相径庭。由于程颐曾有心为已发的言论,胡宏在同曾吉甫论未发之旨时也有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之说。这些思想都影响了朱熹。后来朱熹逐步认识到性
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有毛病,而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的“己丑中和之悟”以后,便修正了前说,提出了心兼已发未发和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统性情的思想。这也是朱熹同张栻等学者相互展开学术交流的结果。
朱子学之已发未发说,是后来韩国李朝李退溪等性理学的核心论题,是韩国其后哲学史的主体意识。
“心统性情”是朱子学心性论的核心和目的。此有二层涵义,即心兼性情和心主宰性情。前者是对心兼性的动静、体用、已发未发的概括;心兼性情,是指心兼性的静、体、未发,兼情的动、用、已发。心兼有性情的两个方面,把性情各自的属性纳入心的兼容之中,就是把性情包括在心之中。
朱熹心统性情论,是在其心兼动静、体用、已发未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宋明理学心性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早先理学心性论的继承、扬弃和发展。朱熹分别吸取了程颐心有体有用的观点和张载“心统性情”的命题,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心统性情”的思想。虽然程颐提出了心有体有用的思想,但是他没有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张载虽然最早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但从现存的材料看不出其命题的具体内容。朱熹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又赋予张载的命题以具体的内涵,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出“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是;‘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是。”①明确把心之体称为性,把心之用称为情,心贯通两端,管摄性情。这便是朱熹的新见解。
真德秀认为,人之性和人之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有是性则有是情。真德秀在《诚意正心之要一》中说:
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仁则是个温和慈爱的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的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樽节的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的道理。凡此四者具以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所用(按即体的表现、作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辞让,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②
由此可见,人之性和人之情是体和用的关系,情是性的表现和作用。因此,要使性之善充分的表现出来,发挥其作用,就要尽性。尽性可以成尧舜。真德秀在《迩言后序》中说:
人之有生虽与物同,而备二气于身,根五常于心,则复与物异,故必如尧舜之善而后可谓尽性。仁、义、礼、智之端有一于缺,则以人跟物其间相去者几希。夫人受此性能于天,犹其受任于朝也。一理弗循谓之违天,一事弗治谓之旷官。旷官可愧也,违天独无愧乎?①
在这里,真德秀把人受性于天比作臣任职于朝,由此推论遵循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原则是人的不可或违的天职,否则即欺慢于天。“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诛”。②因此,“仁、义、礼、智之端有一亏缺”都不算尽性;四端都要充分的表露出来,而且“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谓性之者”。③这就是说,尽性露情是自然的流出,完全出于自觉。
四 格致与力行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倾向。但是,也有讲天人对列的,如荀子说:“凡以(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他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④。在认识论上,朱熹沿着荀子指引的方向往前发展。
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是围绕《大学》提出的“格物”而展开的。朱熹在《答江德功》第二书中说:“自十五六始,知读是书(按《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三十余年。”⑤可见,其都在用力于格物上。格,意为至、极,也可以理解为接近。物即事物。本来主要指事,即伦理道德关系,而朱熹提出“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⑥,包括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因为《大学》提出“格物”概念,却无具体内容。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内容遗失,于是他为之补传。
朱熹指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格物而穷理。他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⑦
朱熹所说的物,是理一分殊的天下万物,包括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当然也有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在这里,朱熹十分明确的把主客观置于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的里程碑,由此《大学》提出的“格物”,便由格心引向格客观事物的方向,为近代科学认识论意识开辟出思路。
朱熹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格物之事。其在《朱子语类》中随时答问,皆讲此四目。如其谓,“且就事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身之内与身外之物,都要格。“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理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格物之目的是穷理。“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有个事物的理,穷之须要周尽。”朱熹与门人问答,每每以“格物穷理”连用,因为物内有理,通过格物而穷其理。在格物穷理中,读书是重要方法。①朱熹之《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中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虽为修养身心之道德原则,也是读书所应遵循的。②
格物就能致知。致,推极、推出之意。《朱子语类》多处谓,推到极处,穷究彻底,真见得其意如此。以类推之,得道(规律)而通其余。格物是逐物而格,致知是逐类旁通,以共性知个性。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是理与心之关系。格物是就个性说,致知是就共性(全体)说。这样说来,两者是合一的,“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无两样功夫”。③此即谓,致知在格物之中,非格物之外另有致知,两者是同时的。
格物致知是与知行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进一步指出,“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④格物致知是知,涵养践履是行。“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⑤由此,朱子学学者深刻论述了知行的问题。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知行先后、难易之争贯串了中国哲学史的始终。朱熹在知行先后上,犹如其理气论一样,本无先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而推论之也可以说知先行后。朱熹反复强调,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二者皆不可偏废。朱熹在《杂学辨》中进一步指出:
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①
真知则必行,因为能行才算真知。此与后来王阳明所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②之知行合一论是一样的。其所不同的,朱熹的知是通过格物穷理所得,而王阳明是由良知所得,不须格物。
在陈淳的认识论中,也特别强调格物穷理。他认为,认识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如果扫除格物一段工夫,如无星之称、无寸之尺,默然存想,是不可能穷理的。他把格物作为认识具体事物取得认识的开端。他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知力行,简称知行。他说: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不过致知力行而已。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因此,他强调致知力行当齐头着力并作,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交进而互发。“故心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益精。”③朱熹有时讲只有明白了义理(知),才能做出合乎义理的事(行),才能以知为标准来判断行的是非;而陈淳明确提出知行当齐头并进。至于陈淳所讲的如何力行和力行的内容,有包括客观事物,而主要仍然是道德的践履。这是朱子学家所共同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黄榦有四个方面的贡献。
(一)提出“物格知至”的命题。他在《复杨志仁》中认为,“物格”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能够推想得明白透彻;“知至”是指人们的知识富足,没有什么不知的。人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的程度,则“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因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又由于性即理,心中具有万事万物之理,“物格知至”,就能达到心中之理全然明白。④
黄榦在《复叶味道》中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了解世界某一部分事物的现象,而是领会(探索)整个世界事物之理,穷理就是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但是,天下事物之理多至不可胜数,尽我们毕生精力也不能件件都穷得,因而必须用致知工夫才行。致知是指从已知之理推及未知之理。只要已知之理积累很多,就可以穷尽未知之理。黄榦在《复杨志仁》中又说:“万物之理各是一样,
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人们的知识的确有许多是从推理得来的。黄榦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①
(二)提出“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的观点。他在《复胡伯量》中说:
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水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②
在黄榦看来,致知能更好地持敬,持敬也能更好地致知。致知与持敬不能相互分离,它们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在这里,黄榦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了。致知是知理,这是认识论;持敬是存心,这是道德修养。上引他的《复叶味道》中又说:“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从“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③由此可见,黄榦的认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上,而是讲体察圣贤言语。
(三)提出“默认实体”的修养原则。他在《答陈泰之》中说:
致知非易事,须要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而真实体段不能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④
黄榦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容易受外界事物的蒙蔽,因而闻见之知不可靠,而只有义理为心之主的德性之知才可靠。这就需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用义理之心去默识体认天理,方才对万事万物的理有所认识。若是一知半解,专从文字上去认识圣贤书上所讲的天理,终日高谈阔论,而真实体段原不曾识;其见不实,其说易差,与动静表里未能合一者,皆谈不上致知。
(四)强调“致知力行”。他在《中庸总说》中说:
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
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天下之理无不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①
黄榦认为,只讲致知不行,而要力行,而且力行要勇往直前,才能确实体会到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才能成全天命所赋予人的善性。
黄榦的认识论是道德实践论,他的认识的目的是完善人的道德品质。在黄榦看来,人的认识对象是天理所赋予的善性,认识的途径是内心体认善性;认识的方法是持敬(即心中时时保持善德)。这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唯理的认识论。
无极、太极是朱子学的重要范畴,是其世界观的出发点,并涉及多方面的关系,首先加以说明。
朱熹把“极”理解为“至”,即“终”、“穷”、“尽”、“竟”之义。朱熹反复讲了这个问题。朱熹说:
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①
他还谓,“极是极至无余之谓。”“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极之义。”枢极指北辰之为天极。“极,尽也。先生指前面香桌,四边尽处是极,所以谓之四极。四边视中央,中央即是极也。”但是,“中不可解做极。极无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极之所为。四向所标准,故因以为中。如屋极亦只在中,为四向所准。”如北极,如宸极,皆然。若只是说中,那就不是极之涵义。②
朱熹认为,太极,因其极至,故谓之太极。上引《语类》中也反复讲了太极的问题。他认为,太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没有去处。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都是没有去处。自外面推进去,到极尽处,没有去处,所以叫做太极。由此,朱熹便得出太极为天地万物之根柢、大源,天地万物之所由出。他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著夫无声臭之妙也。”①
朱熹进一步指出,“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又一图之纲领,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要根柢也。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者哉?近世读者不足以识此,而或妄议之,既以为先生病,史氏之传先生者,乃增其语曰‘自无极为太极’,则又无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尝欲援故相苏公请刊国史‘草头木脚’之比,以证其失。”②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并非无极之后另生太极,太极之上先有无极。无极是形容太极的,即无形而有理之意。他在《答陆子静书》第五书中有曰:
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③
朱熹注《太极图说》之“无极而太极”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原注:是解‘无极’二字),而实造化之极枢,品汇之根柢也(原注:是解‘太极’二字)。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原注:‘有无合一之谓道’)。”④门人杨方对朱熹之注提出异议。朱熹解释曰:
然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气)五(行);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万物,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图之纲领,《大易》之遗意,与老子所谓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矣。⑤
朱熹所谓无极,是讲无之至,而至无之中,乃至有存。无极无声无臭。非太极之外别有无极。太极无极无次序,无先后,无积渐。亦不可将无极便做太极。
周子恐人以太极为一物,故说“无极而太极”,只是无形而有理之意。
朱熹说“无极而太极”,还跟理联系在一起。如其曰:
盖其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①
朱熹门人大都发扬朱熹的这种说法。《北溪语录》录陈淳的有关说法。陈淳认为,“太极只是理,理太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自其冲漠无朕,此浑沦无极之妙也。”真德秀在《论语集篇》中说:
所谓无极而太极者,岂太极之上别有所谓无极哉,特不过谓无形无象而至理存焉耳。盖极者,至极之理也。穷天下之物可尊可贵,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极也。世之人以北辰为天极,屋脊为屋极,此皆有形可见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极为一物,故以无极二者加于其上,犹言本无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阴阳而下丽乎形气矣。阴阳未动之先只是此理,岂有物之可名邪?②
此引真德秀讲的太极与阴阳的关系,全是朱熹之意。朱熹认为,太极在阴阳之中,非在阴阳之外;阴阳亦在太极之中。“所谓太极者,便只是在阴阳里。所谓阴阳者,便只是在太极里。而今人说阴阳上面别有一个,无形无影底物是太极,非也。”但是,太极与阴阳却不能等同,把它们混而为一。阴阳动静,动静皆太极状态,而动静却非太极。朱熹说:
不是(太极)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③
在朱熹看来,阴静是太极之本,而阴静却由阳动而生。“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譬如鼻息,无时不嘘,无时不吸。吸尽则生嘘。理自如此。”④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是动后方生阳,盖才动便属阳,才静便属阴。动而生阳,其初本是静。静之上又须动。不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截然焉两段,先有此而后有彼。只是太极之动便是阳,
静便是阴。方其动时,则不见阴。方其静时,则不见阳。这就是动而生阳的含义。这即是程颐在《经说》中所说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意。
对于朱熹的太极动静,蔡沉从形而上下去解释。他说:
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①
这是蔡沉从抽象与具体上论说太极动静之理的。
黄榦再进一步把太极阴阳与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有太极分阴分阳,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黄榦在《复杨仁志》中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尝在一之先?……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见。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往而非二也。如是则二者,道之体也,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不二哉!……天下之物无独必有二。若只生一,则是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何尝在一之先,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生两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
黄榦这里是批判老子的观点。他认为,“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老氏之所谓道,非吾儒之所谓道也。”②
朱熹不同意用体用理解静动。他认为,太极本来就是涵有动静之理的,却不能以静动分体用。这是因为,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摇动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③朱熹的门人大都沿着朱熹的这个说法发挥。
二 理与气
朱熹在讲太极时,已谓“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理是天地万物之道理。天地万物,则必各有所然之故和其所以当然之则。陈淳说:“理无形状,如何见得?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则是准则,法则。有个确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当合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些不及些,便是则。”④真
德秀在《格物致知之要一》中说:
理未尝离于物之中,知此则知有物有则之说矣!盖盈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视、耳之听,物也;视之明、听之聪,乃则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乃则也。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谓规、矩、准、绳、衡为五则者,以其方圆、平直、轻重,皆天然一家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为之,但循其则尔。如视本明,视而不明,其失其则也。①
这就是说,理指文理、条理,即事物之规则,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规律。
朱熹反复强调,理是实实在在的,并非虚无。这是因为,理与气不离,理在气中,二者相辅而行。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就在气之中。朱熹曰: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②
气不能无理,因凡人物必须有其所以然。理不能无气,因理不是空虚之物。理非别为一物,理存在于物之中。无是气,则是理无挂搭处。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如是浑然一体,非两物并存。朱熹在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曰:“理附搭于气而行。”③所谓理附搭于气,并非指气为主,理为宾,而是理气不离,气亦附理,无主客之分。有门人问动静者,朱子答说: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④
此处把太极、理、气三者的关系都讲清楚了。
陈淳以浑沦释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所谓浑沦,就是像云雾一样茫茫无限。此论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其实,理不外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有主之,曰理是也。然理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
指出个理不离于气而为言耳。”①陈淳强调,虽谓以理为主,但是理在气中,理是通过气而体现出来的。陈淳有把理气合一之倾向。如果说在朱熹那里是把气作为理生物的中间环节,而在陈淳这里则有气直接产生物的气息,具有张载气论的因素。
理气不离不杂并没有否认理先气后。这在朱子学本体论体系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在《朱子语类》答问和《朱子文集》书札中讨论很多。《中庸章句》、《大学或问》、《易学启蒙》亦涉及之。朱熹论太极时曰:“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②在论天地时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③在论人物时曰:“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④在论性时曰:“先有个天理,却有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⑤在论动静时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⑥此处非指理之本身有动有静,而是指如无动静之理,则动静无由施行。在论感应时曰:“未有事物之时,此理已具。少间应处,只是理。……未应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这个道理。”⑦
理先气后并不与理气不离不杂相矛盾,它们是一致的。朱熹所强调的理先气后,是从逻辑上讲的。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说: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⑧
此处先言理在气先,随谓理气不离。朱熹在《答刘叔文》第一书中说: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①
这里明确讲逻辑推论。在朱熹看来,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是理在先气在后。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在《朱子语类》讲到这个问题时,冯友兰于此言下案语曰:“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若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②朱熹理气不离不杂与理先气后之说,具有非常深刻的逻辑学的意义。
不仅如此,在理气关系上,朱熹还强调理生气,有是理然后生是气。此“生”非生“子”之生,而是“生事”、“生心”之“生”,含有本原之意,亦有存在所由之意,即上面所说的必然之性,是指“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论运行,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会他不得。如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若论本原,则可谓理强气弱,因理是气之必然性。在此意义上,理是气之主宰。其门人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者否?”朱熹答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③此主宰非有意之主宰,而是如程颐所谓“天地无心而成化”④之主宰,亦即理决定气之種種存在与性质之主宰。
对于理气关系,蔡沉以其数理论加以解释。其《洪范皇极·内篇》中反复强调,“有理斯有气,气著而理隐。有气斯有形,形著而气隐。人知形之数,而不知气之数;人知气之数,而不知理之数。知理之数,则几矣。动静可求其端,阴阳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万物可求其纪;鬼神知其所幽,礼乐知其所著。生知所来,死知所去。《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在蔡沉看来,理之数是“几”,即包含了理生气、气生形的动因。他说:
有理斯有气,有气斯有形,形生气化而生生之理无穷焉。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赜。复土之陵,积水之泽,草木虫鱼,孰形孰色。无极之真,二五之数,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测其神,莫知其能。⑤
蔡沉所表达的朱子学本体论之太极、理、气诸范畴与朱熹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加了个“数”。蔡沉的世界图式论以数作为基础,始终贯串着数之关系。
天即理,是朱熹理学的本色。“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①
朱熹据《易·系辞传》之“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得出“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②
既然天地以生物为心,那么人、物得之必以为心。一个天地之心是指大宇宙,一人一物之心是指小宇宙。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人心之理和万物之理都是由天理分殊出来的。
朱熹据当时北宋理学家的理气观点,又参照释、道的有关说法,便明确了“理一分殊”之意。朱熹说:
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里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圣贤之学,非老氏之比。老氏说“通于一万事毕”,其他都不说。少间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③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如排数器水相似:这盂也是这样水,那盂也是这样水,各个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然打破放里,却也只是个水。此所以可以推而无不通也。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④
此“月印万川”,亦即佛家所常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就是说,人心之理与万物之理都是由天理分殊出来的。显然,朱熹的理一分殊论是吸取了释、道之合理思想的。
朱熹给传统的天人合一赋予理一分殊的新意,找到了天是如何衍化出人、物的,使中国人的世界观严密完整,更富有特色。朱熹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创见。他说:熹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则见“仁”字与“心”字浑然一体之中,自有分别,毫厘有辨之际,却不破碎,恐非如来教所疑也。①
此“臆见”是由释氏之“月印万川”启发出来的。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仁,仁则生。仁为众善之首,仁自然又生出义礼智等美德。
朱熹的理一分殊论,真德秀用体用一元来解释。他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但是皆为根本理之体现。根本的理是本体,每个事物所具有的理是万殊,都是根本理的作用和运用,而且是根本理的缩影。根本的理和万殊的理都是道,因此是体用一元的。这就是真德秀所说的“至诚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殊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真德秀又说:
天下之理一,而分则殊。凡生于天壤之间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气者也,是之谓理一。然亲者吾之同体,民者吾之同类,而物则异类矣,是之谓分殊。以其理一,故仁爱之仁无不遍;以其分殊,故仁爱之施则有差。以亲亲之道施于民,则亲疏无以异矣,是乃薄其亲;以仁民之道施于物,则贵贱无以异矣,是乃薄其民。故于亲见则亲之,于民则仁之,而于物则爱之。合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异于杨、墨也。②
在真德秀的理一分殊论中,包含了一般与个别、一与多的辩证法因素。但是,真德秀有时认为,万殊分别完美无缺地体现了一理,有把一般与个别、一与多等同之嫌,而且他把理一分殊主要分析道德伦理关系,其辩证法是不彻底的。
朱子学学者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由原先孔子的伦理内涵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儒学建立起完备精密的形上学系统。他们用“理一”统摄“万殊”,把儒家的本体论、人生观、知行观糅合成一个整体。
三心与性情
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提出理一而万殊,把一理与万殊联系起来。那么,一理与万殊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朱子学家们的心性论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他们依据《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即人、物之性是由天理所赋予的,心是
神明之舍、一身之主宰,即心是认识和道德之主体。作为认识的主体,心要和理、事物发生关系。朱熹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①心作为道德主体,又有道德与非道德意识,便有道心与人心的问题。
朱熹的心性论,更多地得之于释、道之说。对此,朱熹有反复的论说:
(朱熹)因举佛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曰:“朴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看他是怎么样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为他挥下也。此是法眼禅师下一脉宗旨如此。今之禅家皆破其说,以为有理路,落窠臼,有碍正当知见。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之不落窠臼不坠理路。妙喜之说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转不如此说时。②
此是说明儒、释之心性说的相似处。朱熹之心性言论,大都似慧能《坛经》等说法,如慧能在《坛经》中谓“万法在诸人性中”、“自心见性”,③朱熹则谓“若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④、“性之理包在心内,到发时却是性底出来”⑤,等等,比比皆是。朱熹说:
佛学其初只说空,后来说动静,支蔓既甚,达摩遂脱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静见理。此说一行,前面许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难为抗衡了。今日释氏其盛极矣。但程先生所谓“攻之者,执理反出其下”。吾儒执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胜也。⑥
朱熹把《坛经》等释、道书中的心性、心体、心量、明心见性、心静见理等由“虚无”放置于“实有”上,反其意而用之,成为自家的珍品,然后“执理”再与其对抗,自然就显得对方空洞贫乏无力了。
在朱熹看来,儒与释、道之学在心性问题上貌同而神异,不同的只是内涵。要在释、道心性的形式中填入儒家的内容。此在《朱子语类》中有反复的论说。
他认为,“吾以心与理为一,彼(释、道)以心与理为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虽说心与理一,无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是见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学》所以贵格物也。”基于这种认识,朱熹便广泛地论及释、道之心性说,录己之所需要者。据《朱子语类》记载:
问释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这性,他说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便是此性。如口会说话,说话底是谁?目能视,视底是谁?耳能听,听底是谁?便是这个。其言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他说得也好。又举《楞严经》波斯国王见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禅家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只要你见得,言下便悟,做处便彻,见得无不是此性。也说“存心养性”,养得来光明寂照,无所不遍,无所不通。唐张拙诗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云云。又曰:“实际理地不受一廛,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他个本自说得是,所养者也是;只是差处便在这里。吾儒所养者是仁义礼智,他所养者只是视听言动。……只认得那人心,无所谓道心,无所谓仁义礼智。……他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云云。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至神鬼神仙士农工商技艺,都在他性中。他说得来极阔,只是其实行不得。①
朱熹认为,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这是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以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此只是源头处错了。这就是说,释者人心之说有可取之处。人之道德理性亦含于心中,当心(心官、报身)起用时,心不仅有自然之思之妙用,且能思其所当思当行,有知是非之良知良能。理学家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性即天理,无有不善。而理与气便形成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同时受理与气的作用,因气有清浊、偏正,所以气质之性是天理与人欲的综合。
上面是讲朱熹论儒释心性之不同和相互关系。下面具体说明朱子学的心性论。先看其心论。朱熹谓,“有知觉谓之心。”②这是讲心对外物有感知,能对外物有反映。朱熹说:“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①是讲心有思虑功能。朱熹又说:“心,主宰之谓也。”②此主宰是指主于一身和主于万事,前者说的主宰是感觉器官,后者说的是心具有能动作用,使事物能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对此,真德秀在《天性人心之善》中说得更明确,认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心其能穷天理而无不立者也。”③这是讲心的认知能力。
上面讲的是主观意念之心,是人心。此外,还有天地之心。人心是天地之心的一部分。所谓天地之心,是指天地生物之心,是宇宙万物和包括人心在内的天下之心存在的总根源,即万物产生的本原。天地之心表现在人方面则为人心,人心便是人得天地之心而成其为己心。朱熹说:
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贯。④
这是说,天地之心和人心贯串着一条仁的脉络。所谓“心德”,即仁义礼智心之四德,由仁统帅之。
上面讲的人心,其一个含义是有知觉。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心,按其知觉的来源和内容便可有两种不同的心。朱熹说:
或问“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著。微,亦微妙之义。⑤
道心是指以义理为人内容的心,仁义礼智为善,道心亦为善。而人心则指的是原于耳目之欲的心。人生有欲,饥食渴饮,虽圣人不能无心,故人心不是全不好的,可为善亦可为不善。朱熹认为,人是形气和性命结合的产物,人生有欲,这是人不可避免的;而心中有理,这是上天所赋予的。所以,人心与道心是人人所有之的。朱熹说:
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够无人欲;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够无道心。①
道心是以义理为内容的,原于性命之正,道心至善;人心是以耳目之欲为内容的,生于形气之私,人心有善有恶。人心与道心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是人之一心的两种表现。
对此,陈淳有更深入的综合说明。他说:
心者,一心之主宰也。人之四肢运动,手持脚履,与夫饥思食、渴思饮、夏思葛、冬思裘,皆是其心为之主宰。今如心羔的人,只是此心为邪气所乘,内无主宰,所以日用间饮食动作皆失其常度,与常人异。理义都丧了,只空有个气,仅往来于脉息之间,未绝而已。大抵人得天地之理为之性,得天地之气为之体,合理与气方成这个心,有个虚灵知觉,便是心所以为主宰处。然这个虚灵知觉,有发于理者,有发于气者,各有不同。②
在陈淳看来,心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心能认识客体。如果认识正确,就会有正确的动机和行为,它就是道心;反之,如果认识错误,就会产生不正确的动机和行为,它就是人心。陈淳又说:
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其所以为虚灵知觉,由形气而发者,以形气为主,而谓之人心;由义理而发者,而谓之道心。若目能视,耳能听,口能言,四肢能动,饥思食、渴思饮、冬思裘、夏思葛等类,其所发皆本于形气之私,而人心之谓也。非礼勿视,而视必思明;非礼勿听,而听必思聪;非礼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礼勿动,而动必思义;食必有礼……饮必有节……寒不敢裘,暑毋褰裳,其所发皆源于义理之正,而道心之谓也。③
陈淳认为,性是天理,它是至善的。从性流出来的是道心,从物欲触发出来的是人心。道心是全善的,而人心则是有善有恶。“从理上发出来的”,就是正确的行为和动机,亦即是仁、义、礼、智之心,就是道心。“从形气上发出的”,就是有不正确的行为和动机,亦即饥思食、渴思饮之类的心,就是人心;道心对于饮食,要从理上考虑当不当饮食,如不食嗟来之食。在朱熹那里,注重在善恶上解释人心、道心;而陈淳则是注重在出发点上解释人心、道心,以感官的天然倾向为人心,以伦理的天然倾向为道心,更注重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因此,陈淳发展了朱熹关于人心、道心的思想。在陈淳看来,出于人自私目的的是人心,出于义理目的是道心。人心总是自私的,它是臬危兀危不安的;道心总难
免遭受人心的蒙蔽,不易充分显露出来。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在于努力使道心处于支配的地位,而使人心服从道心的支配。
上面讲的是心。再看看他们对性的认识。朱熹在《玉山讲义》中深刻地叙述了性的问题。他说: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凡此四者(仁义礼智)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慾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应正谓此也。……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①
《玉山讲义》是朱熹晚年成熟著述,全面概括地论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是治朱子学者必读之书。人之情是与性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认为,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性为静、未发、体;而情的内涵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以及喜、怒、哀、乐等,情为动、已发、用。朱熹在《答胡伯逢》第四书中说:
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之言,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己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性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有改者也。②
未发是指仁义礼智之性未表现出来的状态,即思虑未萌时心之状态;已发是指思虑已萌时心之状态。朱熹强调,善贯串于未发、已发两端,即情发而中节,符合性的原则,即善的表现。
朱熹是从心兼体用上理解心兼已发未发的。他认为,由于心统情性,心有体用,故心跨已发未发两头。这是从逻辑上推论。朱熹在《答林泽之》第六书中说:
未发只是思虑事物之未接时,于此便可见性之体段,故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也;发而中节,是思虑事物已交之际,皆得其理,故可谓之和,而不可谓之心。心则通贯乎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①
未发已发是心体流行一静一动两个不同的阶段。可见,心之未发与心之体、心之静相联系;心之已发与心之用、心之动相沟通。心具有未发、已发两种状态,即指心兼未发、已发。
需要指出,心之未发时可见性之体,性具于心,但心不等同于性;心之已发时可见情之著,情通于心,但心不等同于情。虽然心贯通于未发之性和已发之情,但心与性、情有各自不同的确切涵义和规定性,彼此不能相混。朱熹在《已发未发说》中说:
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须穷索,但当此之时,敬以持之,使此气象常存而不失,则自此而发者,其必中节矣。此日用之际,本领工夫,其曰“却于已发之处观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动,而致扩充之功也。一不中,非性之本然,而心道或几乎息矣。故程子于此,每以“敬而无失”为言。②
此指出心之未发可谓之中,然不可谓之性。心之已发,谓之和,情为心之用,但情也并不等同于心。
朱熹心兼已发未发,即心贯通于已发未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最后确立的过程。在已发未发问题上,开始时朱熹受程颐及胡宏思想的影响,持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这与他自己后来形成的心兼已发未发的思想大相径庭。由于程颐曾有心为已发的言论,胡宏在同曾吉甫论未发之旨时也有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之说。这些思想都影响了朱熹。后来朱熹逐步认识到性
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有毛病,而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的“己丑中和之悟”以后,便修正了前说,提出了心兼已发未发和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统性情的思想。这也是朱熹同张栻等学者相互展开学术交流的结果。
朱子学之已发未发说,是后来韩国李朝李退溪等性理学的核心论题,是韩国其后哲学史的主体意识。
“心统性情”是朱子学心性论的核心和目的。此有二层涵义,即心兼性情和心主宰性情。前者是对心兼性的动静、体用、已发未发的概括;心兼性情,是指心兼性的静、体、未发,兼情的动、用、已发。心兼有性情的两个方面,把性情各自的属性纳入心的兼容之中,就是把性情包括在心之中。
朱熹心统性情论,是在其心兼动静、体用、已发未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宋明理学心性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早先理学心性论的继承、扬弃和发展。朱熹分别吸取了程颐心有体有用的观点和张载“心统性情”的命题,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心统性情”的思想。虽然程颐提出了心有体有用的思想,但是他没有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张载虽然最早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但从现存的材料看不出其命题的具体内容。朱熹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又赋予张载的命题以具体的内涵,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出“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是;‘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是。”①明确把心之体称为性,把心之用称为情,心贯通两端,管摄性情。这便是朱熹的新见解。
真德秀认为,人之性和人之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有是性则有是情。真德秀在《诚意正心之要一》中说:
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仁则是个温和慈爱的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的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樽节的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的道理。凡此四者具以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所用(按即体的表现、作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辞让,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②
由此可见,人之性和人之情是体和用的关系,情是性的表现和作用。因此,要使性之善充分的表现出来,发挥其作用,就要尽性。尽性可以成尧舜。真德秀在《迩言后序》中说:
人之有生虽与物同,而备二气于身,根五常于心,则复与物异,故必如尧舜之善而后可谓尽性。仁、义、礼、智之端有一于缺,则以人跟物其间相去者几希。夫人受此性能于天,犹其受任于朝也。一理弗循谓之违天,一事弗治谓之旷官。旷官可愧也,违天独无愧乎?①
在这里,真德秀把人受性于天比作臣任职于朝,由此推论遵循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原则是人的不可或违的天职,否则即欺慢于天。“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诛”。②因此,“仁、义、礼、智之端有一亏缺”都不算尽性;四端都要充分的表露出来,而且“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谓性之者”。③这就是说,尽性露情是自然的流出,完全出于自觉。
四 格致与力行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要倾向。但是,也有讲天人对列的,如荀子说:“凡以(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他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④。在认识论上,朱熹沿着荀子指引的方向往前发展。
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是围绕《大学》提出的“格物”而展开的。朱熹在《答江德功》第二书中说:“自十五六始,知读是书(按《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三十余年。”⑤可见,其都在用力于格物上。格,意为至、极,也可以理解为接近。物即事物。本来主要指事,即伦理道德关系,而朱熹提出“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⑥,包括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因为《大学》提出“格物”概念,却无具体内容。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内容遗失,于是他为之补传。
朱熹指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格物而穷理。他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⑦
朱熹所说的物,是理一分殊的天下万物,包括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当然也有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在这里,朱熹十分明确的把主客观置于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的里程碑,由此《大学》提出的“格物”,便由格心引向格客观事物的方向,为近代科学认识论意识开辟出思路。
朱熹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格物之事。其在《朱子语类》中随时答问,皆讲此四目。如其谓,“且就事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身之内与身外之物,都要格。“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理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格物之目的是穷理。“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有个事物的理,穷之须要周尽。”朱熹与门人问答,每每以“格物穷理”连用,因为物内有理,通过格物而穷其理。在格物穷理中,读书是重要方法。①朱熹之《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中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虽为修养身心之道德原则,也是读书所应遵循的。②
格物就能致知。致,推极、推出之意。《朱子语类》多处谓,推到极处,穷究彻底,真见得其意如此。以类推之,得道(规律)而通其余。格物是逐物而格,致知是逐类旁通,以共性知个性。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是理与心之关系。格物是就个性说,致知是就共性(全体)说。这样说来,两者是合一的,“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无两样功夫”。③此即谓,致知在格物之中,非格物之外另有致知,两者是同时的。
格物致知是与知行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进一步指出,“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④格物致知是知,涵养践履是行。“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⑤由此,朱子学学者深刻论述了知行的问题。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知行先后、难易之争贯串了中国哲学史的始终。朱熹在知行先后上,犹如其理气论一样,本无先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而推论之也可以说知先行后。朱熹反复强调,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二者皆不可偏废。朱熹在《杂学辨》中进一步指出:
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①
真知则必行,因为能行才算真知。此与后来王阳明所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②之知行合一论是一样的。其所不同的,朱熹的知是通过格物穷理所得,而王阳明是由良知所得,不须格物。
在陈淳的认识论中,也特别强调格物穷理。他认为,认识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如果扫除格物一段工夫,如无星之称、无寸之尺,默然存想,是不可能穷理的。他把格物作为认识具体事物取得认识的开端。他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知力行,简称知行。他说: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不过致知力行而已。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因此,他强调致知力行当齐头着力并作,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交进而互发。“故心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益精。”③朱熹有时讲只有明白了义理(知),才能做出合乎义理的事(行),才能以知为标准来判断行的是非;而陈淳明确提出知行当齐头并进。至于陈淳所讲的如何力行和力行的内容,有包括客观事物,而主要仍然是道德的践履。这是朱子学家所共同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黄榦有四个方面的贡献。
(一)提出“物格知至”的命题。他在《复杨志仁》中认为,“物格”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能够推想得明白透彻;“知至”是指人们的知识富足,没有什么不知的。人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的程度,则“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因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又由于性即理,心中具有万事万物之理,“物格知至”,就能达到心中之理全然明白。④
黄榦在《复叶味道》中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了解世界某一部分事物的现象,而是领会(探索)整个世界事物之理,穷理就是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但是,天下事物之理多至不可胜数,尽我们毕生精力也不能件件都穷得,因而必须用致知工夫才行。致知是指从已知之理推及未知之理。只要已知之理积累很多,就可以穷尽未知之理。黄榦在《复杨志仁》中又说:“万物之理各是一样,
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人们的知识的确有许多是从推理得来的。黄榦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①
(二)提出“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的观点。他在《复胡伯量》中说:
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水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②
在黄榦看来,致知能更好地持敬,持敬也能更好地致知。致知与持敬不能相互分离,它们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在这里,黄榦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了。致知是知理,这是认识论;持敬是存心,这是道德修养。上引他的《复叶味道》中又说:“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从“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③由此可见,黄榦的认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上,而是讲体察圣贤言语。
(三)提出“默认实体”的修养原则。他在《答陈泰之》中说:
致知非易事,须要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而真实体段不能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④
黄榦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容易受外界事物的蒙蔽,因而闻见之知不可靠,而只有义理为心之主的德性之知才可靠。这就需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用义理之心去默识体认天理,方才对万事万物的理有所认识。若是一知半解,专从文字上去认识圣贤书上所讲的天理,终日高谈阔论,而真实体段原不曾识;其见不实,其说易差,与动静表里未能合一者,皆谈不上致知。
(四)强调“致知力行”。他在《中庸总说》中说:
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
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天下之理无不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①
黄榦认为,只讲致知不行,而要力行,而且力行要勇往直前,才能确实体会到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才能成全天命所赋予人的善性。
黄榦的认识论是道德实践论,他的认识的目的是完善人的道德品质。在黄榦看来,人的认识对象是天理所赋予的善性,认识的途径是内心体认善性;认识的方法是持敬(即心中时时保持善德)。这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唯理的认识论。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