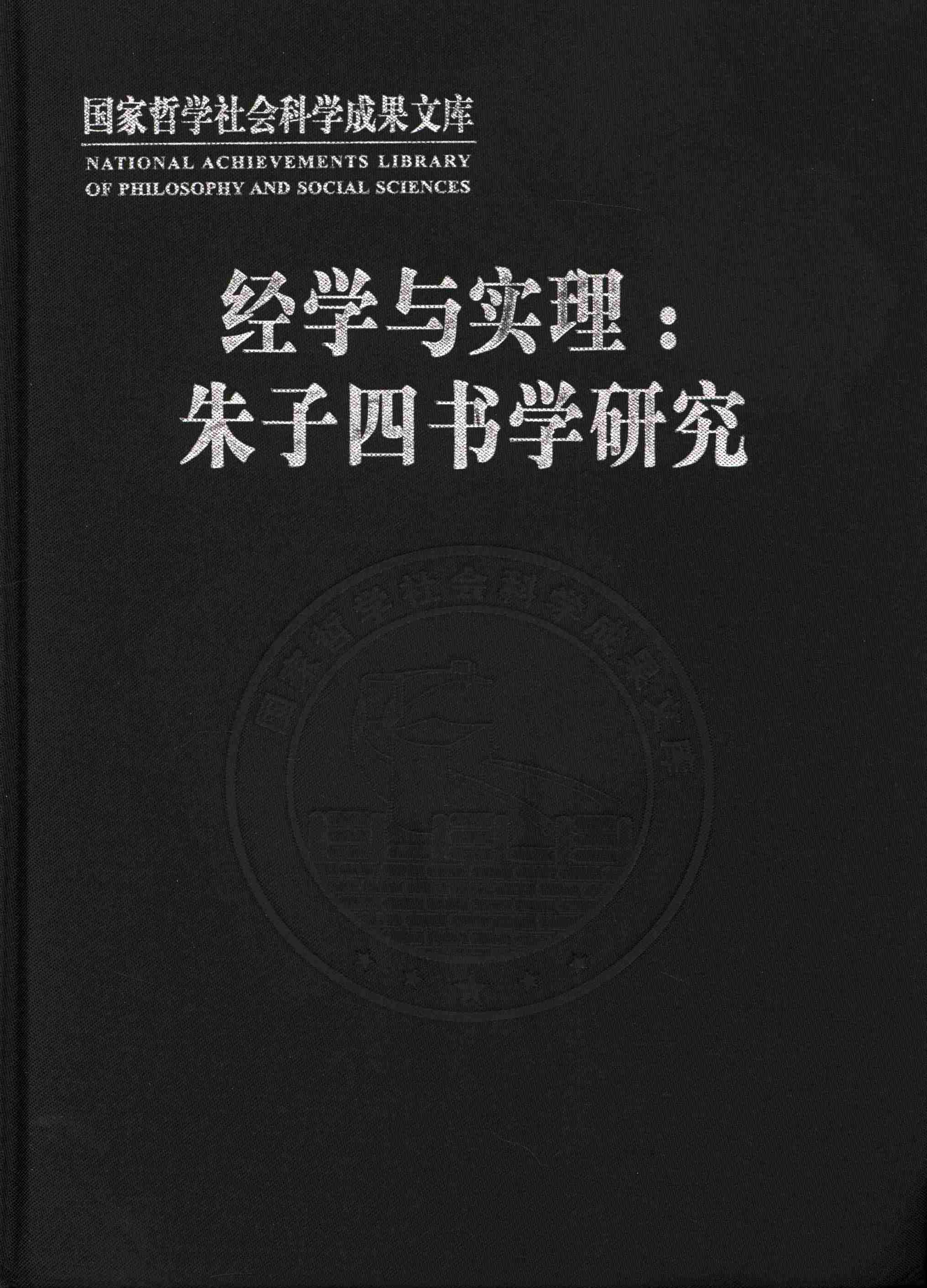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七章 朱子四书学的传承发展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920 |
| 颗粒名称: | 第七章 朱子四书学的传承发展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43 |
| 页码: | 538-580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四书学的传承发展情况的具体介绍,内容主要包括“字义体”:《四书》范畴学之演变、勉斋《中庸》学对朱子的接续与发展、美国当代朱子《四书》研究:以贾德讷为中心等。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第一节 “字义体”:《四书》范畴学之演变
中国哲学以重直觉体悟、轻逻辑论证为特点,哲学家对哲学的看法常以口语即兴的形式表达,缺乏对范畴的确切界定。宋代理学在继承传统儒学固有特色的同时,亦体现出对范畴之学的关切,出现了专门诠释理学范畴的“字义”体。探究这一“字义”体的演变历程及特征,有助于认识理学的范畴之学和四书学,增进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朱子对四书的精密注释实为“字义”学之先导,程端蒙《性理字训》发其端,陈淳《北溪字义》显其成,三传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扩其域。私淑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五传朱公迁《四书通旨》则皆以“字义”为纲,类聚经书正文,分别形成“字义”+注疏、“字义”+“经疑”的综合体。朱子门人后学创造出来的“字义”体,构成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样式,具有类聚范畴、专注义理、定位蒙学、理学指南的特质。尽管其“摆落章句”“类聚字义”之做法未见得为朱子所认可,然其直指范畴的诠释方式,实为中国哲学范畴之学、四书学的发展,显示出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之继承与创新。
一 开端之作:《性理字训》
理学“字义”学与朱子密不可分。朱子生平好章句学,重范畴辨析,凝聚其毕生心血的《四书章句》对诸多概念有着精密界定,体现出“浑然犹经”的特色,达到了“字字称等”的地步。为此,朱子门人后学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体裁对之作了多样阐释,发端于程端蒙、大成于陈淳、变异于真德秀的“字义”体,则构成阐释朱子《四书》的一种新样式。
朱子素重童蒙教育,撰有《童蒙须知》等著作。“字义”即弟子承此思想而作,意在教化童蒙,为童蒙日后德性养成打下基础。程端蒙《性理字训》言:“凡此字训,搜辑旧闻。嗟尔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义。……圣贤可致。”①可见该书乃是初学小子掌握理学名义,成就圣贤的启蒙之作。朱子又称其为《小学字训》。该书仅380字,以四字句形式对理学30个主要范畴作了精炼概括,简明扼要,易于记诵是其最大特点。如“仁义礼智”仅用三句短语训释,“诚、信、忠、恕”仅以四字训释,简略至极。朱子对该书有两种看法:既高度称许其训释之功堪比古代第一部词典《尔雅》,认为该书“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②。又对其简明有余、精确不足有所批评。他曾与黄榦论及此点:“如仁只说得偏言之仁,不曾说得包四者之仁。”③认为该书“无所偏倚谓之中”仅阐发了在中义,而无时中义。“仁”仅阐发了偏言意义之仁,而未顾及专言之仁的统领义。此非著者理解力不足,而是为定位训蒙所累。
尽管该书有粗疏偏颇之不足,然作为“字义体”的首创,其先导之功仍具不可忽视之意义。就选词论,该书30个范畴几为后出同类著述全部取用,构成“字义”体的核心范畴。就内容论,所选范畴侧重心性、道德、工夫,缺乏天道本体、治道外王,此亦与其定位童蒙有关。此外,该书漏收“意”这一心性论重要范畴。其范畴训释多见于朱子《四书》,如以“真实无妄”释诚,“主一无适”释敬等。该书亦有其创新:一是补充朱子所未明言者。如把“智”训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谓”,突出智之“别”义。二是编排颇具匠心,把“命”置于所有范畴之首,居于“性”之前,《北溪字义》亦袭此。
比较《性理字训》与《北溪字义》范畴及编排,可谓“大旨相同”。《字训》范畴大致分三组,命、性、心、情、才、志前六个为心性组,《北溪字义》与其序一致;“仁义”至“孝悌”诸范畴为德性工夫组。《字义》则有不同:一是将具内在联系的两个(或更多)分说的范畴合并为一个范畴。二是调整范畴次序。如《字训》“信”与“诚”相邻,《字义》则置“信”于五常,同时又在“忠信”中予以讨论,而将“诚”与“敬”相邻。三是范畴不相应增多。《字义》另列“恭敬”,取消《字训》之“孝”“悌”“一”。《字训》天理人欲等四对范畴为成德境界组。《字义》则自“道”始为下卷,论本体、成德、鬼神、异端。并增加了《字训》所无的皇极、礼乐、经权、鬼神、异端。盖在陈淳看来,这些皆是圣贤成德境界所应有之效用,乃内圣必备之外王。
二书之差别主要见诸义理阐发之深浅。《字训》纯为初学者设,“颇为浅陋”,《北溪字义》的出现使得《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已无著录价值,故仅将之归为存目,甚至因该书水平不高而怀疑该书为村塾先生所作,这是缺乏历史眼光而有失公平的。①
二 典范之作:《北溪字义》
《北溪字义》以其“抉择精确、贯串浃洽”(陈宓序语),将“字义”从童蒙之学提升至“经学之指南、性理之提纲”(顾仲序语)的高度,树立了“字义体”的典范,标志着诠释《四书》新样式的形成。学界诸贤对该书的研究已有诸多重要成果,今拟就若干问题再加讨论。
题名异议。关于该书题名,两位前辈学者有不同看法。邱汉生认为该书应命名《四书性理字义》方全面确切,他说:“从书的内容考察,当以名《四书性理字义》为较确切、周匝。盖《四书》言其范围,‘性理’标其性质,‘字义’指其体例。”②陈荣捷则主张应名《北溪字义》或《性理字义》,不赞同《四书字义》之名,理由是四书不足以概括其中三个范畴:太极、释、道。邱氏已注意及此,认为既然《四书》能概括该书绝大部分条目范围,就足以作为书名,个别范畴无法概括并无关系。他特别以“羽翼《四书集注》的《四书性理字义》”为题,提出《北溪字义》是“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等二十五个范畴,逐条加以疏释论述的书。……是理解朱熹《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①。愚以为,“字义”所关注的朱子“四书”,是以《四书集注》为中心,辅之以朱子有关四书论述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太极”等个别范畴实亦纳诸其讨论范围内。以四书命名,并无不妥,可足显其醒目之效。
该书实为阐释《四书集注》的新样式。古人对此早有高论。施元勋序据《近思录》为《四书》阶梯之说,提出《北溪字义》为《四书章句集注》的“阶梯”说。“亦愿今之读《章句集注》者,以是为阶梯尔。”②宋李昴英序认为二书是源流关系,学者当“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邱汉生进而认为该书是“解释《四书集注》的第一部书”。③该书是否是第一部并不好说。朱门弟子对朱子思想的体会皆不离对《四书集注》的研习,黄榦等对该书皆有阐发之作,虽未完整留存,但多少保留于注疏中。再则,该书体例并非解释《集注》之书。历来目录著作,皆不置其于经部,而视为童蒙类置于小学类或史部,《四库》即置其于史部。故就形式论,该书非阐释《集注》之作;就实质论,可视为阐释《集注》范畴的专题之作。
该书范畴之选取及其编排,成为近来学界的关注点。张加才提出可据该书卷上、卷下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部分,进而再分为心性论、道德论,理本论、教化论、批判异端论五部分。④邓庆平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上卷所选之‘字’属于性情论、道德修养论的概念,下卷为本体论、境界论和批判异端。”并在范畴归属上,将张加才教化论的“义利”划归“批判异端”。⑤
二位学者力求找出二十六个范畴逻辑划分的努力,总令人感觉不踏实。比如从何种意义上把“皇极”视为本体论范畴?“义利”如何属于批判异端而非成德之目?窃以为,对其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仅能大概而论,不可过分较真。首先,该书非陈淳有意识的构思之作,乃弟子王隽所录讲学结果。其卷次、字次编排是否有精心构思,实可存疑。其次,该书毕竟兼有启蒙性质,以阐释朱子《四书》范畴为中心,追求范畴之精当解释,至于范畴之联系,非其考虑重心所在。最后,即便有内在“逻辑”,恐亦非直线式,非此即彼的逻辑,古人讲求融合、通透、灵活、贯通,逻辑以“两即”为特色①。该书正体现了“玲珑透彻”的相即性。陈淳指出,道理是贯通循环的,当对道理的领悟进入圆通熟透之境界,道理之表述则横竖皆可,不拘于一。“此道理循环无端,若见得熟,则大用小用皆宜,横说竖说皆通。”②
该书开篇即告知理解此书之法,言“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渐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单看本字须亲切,合观多字须玲珑透彻。玲珑具清越、明彻、精巧、灵活诸义,它提醒读者应注意诸范畴间同中有异、分中有合、相互渗透的特点,做到明而不乱,灵而不滞。元儒陈栎对该书的把握亦是玲珑精透,称《字义》一书玲珑精透。③此一特色与陈淳范畴诠释原则亦相应,他在阐发“道”时提出一重要观点,即“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方可”④。他以实例为据,指出同一“道”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有“就造化根原上论”和“就人事上论”之别。可见,若过分追求该书范畴间严密的逻辑体系,恐不合古人立言宗旨。
关于诠释形式。《北溪字义》成为“字义体”典范,不是因其释字多,篇幅长,而是因其“简而该,切而当”的阐释特色,为“宋代理学最简明之叙说分释”⑤。全书仅收26个范畴,为同类著作最少,然看似范畴少,实则如细致析分,恐亦近乎百个,因其条目最多也。
该书诠释最大特色在于注重范畴的界分与脉络。陈淳认为“字义”间具有某种类似脉络的连结关系,对某一“字义”的精确“界分”,须结合其脉络进行,置“界分”于“脉络”中。一方面,精于“界分”,突出比较,构成该书特出之处。该书对范畴异同辨析高度重视,常将之置于正面下定义之前。如诚,首言“诚字与忠信字极相近,须有分别”①。鉴于字义的复杂丰富性,陈淳在“五常”的阐释中提出“竖观”“横观”“错综观”“过接处观”等多角度的字义审查方法。所谓“竖观”,即五常各自有其对应之物件和含义,略似于分而论之,强调每个范畴的独立性;所谓“横观”,指用综合的眼光考察范畴间联系,近乎合而观之,突出范畴的有机整体性。所谓“错综观”,凸显的是范畴既具有内在的独立自主性,又与其他范畴存在相互错综、彼此包含、内在融贯的一体关系,其实即“横竖并观”。所谓“过接处观”,亦是就范畴间联系而论,强调在某一范畴中已内在“酝酿”着相关范畴,范畴之间是相生互具的。
析一为二的“二义”法。陈淳大量运用“界分为二”法,最典型的是直接将范畴两种含义点明,如“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次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将某一范畴切分为二,多是成对范畴,如理气、心事、心理、内外、天人、自然用力等,具体可参其对诚、忠恕、仁等字义的解释。还有“就某方面而论”者,如命可分为“就人品类论”“就造化上论”两类。较常用的区别术语有“正面一边”“言上事上”“浑沦分别”等。与此同时,陈淳亦再三提醒应注意范畴间的脉络关联,不可将之视为“判然二物。”如“忠信非判然二物”。“非二”要求从范畴间一体关系出发,强调“即一”。他特别批评韩愈对仁义、道德理解之误在于判二者为二物,“是又把道德、仁义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②。
陈淳对“字义”脉络与界分辩证关系有深刻把握,提出“浑然中有界分。”如不加以细致分析,则无法看清各字义的独特意义,如仅顾及个别字义而不将之置于更大范畴之网,则无法把握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盖范畴之间“元自有脉络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③最合理的方式是将“界分”置于范畴之网,既能把握范畴之间的联系,体会其相似性,又能加以精确区分,掌握各范畴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引起字义的乱用,即“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①。陈淳还强调了处理范畴关系的灵活性,提出“不可泥着”。
三 扩充之作: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
(一)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
元程若庸曾问学饶鲁,为朱子三传,他对《性理字训》加以增补,将范畴扩充至183个,此后明代朱升又据袁甫说增加“善”字,为184个。该书特色是大大扩充收字范围,数量为同类之冠,且将所收字明确分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大门类,在每门末加以总结。《性理字训》所收范畴主要见于该书情性、学力、善恶三门,故其他三门几全为增补。与前此二家置“命”于首不同,它以“太极”居首,同于《近思录》之首列“道体”。程氏认为,“太极”作为造化本原的字义,具有广大精微的特点,对初学而言具有难度。将其列之于首,希望学者通其名义,知学之标的所在,以之为终生求学之目标。该书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的安排,展现出由天道本原,经由人之心性、工夫、德性、境界,落实于治理教化的过程,全面周到。其新增范畴多取自《四书》,有些已为《近思录》所取,可证该书确是参考了《近思录》。此外,不少范畴如“理一、分殊”等直接取自理学话头,显示出字义体阐释理学四书的宗旨。
该书仍停留蒙学水平。各范畴既孤立无联系,又多交叉重复,甚者同一“字”作为两个范畴出现,如造化门分列两个“天”,分别作为自然形体意义上和义理意义上的天。此并非偶然,乃故意为之。该书对“道”的处理亦如此。一是造化门生成万物无声无臭的形而上之道,二是情性门作为人伦事物当然之理的共由之道,即伦道。此外,该书尚另设有天道、人道、达道、小道四个范畴,前三者皆属于“情性”门,“小道”则属“善恶”门。照《北溪字义》的处理,应属于同一字的不同义项,作为两个“字”处理,显然不合适。无怪乎四库讥其“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该书虽仍拘泥于四言童蒙式,但影响颇大,成为理学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本,元朱升将之与《名物蒙求》等并列为小学“四书”。后世多以该书取代《性理字训》。元程敏政认为该书体现了朱子童蒙教育思想,要求童蒙八岁入学前,每日读该书三五段,视之为替代世俗《千字文》等蒙学教材的最佳读本。“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日读《字训》纲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①此外,元史伯璿《管窥外篇》提出该书有白本、注本之分,其流传、异同颇值留意。
(二)陈普《字义》
陈普,字尚德,号石堂,宁德人,《续修四库全书》收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据《字义后序》可知,陈氏学于浙江韩翼辅,韩氏为辅广之徒,故陈普当为朱子三传。《遗集》卷九所收《字义》一书,是陈普与弟子讲说讨论的结集,选取平日讲说中意味深厚亲切、简洁明白,可成字义者,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布局,共收字义153个,因今本残缺,实存138个,全文约11000字,“多于程正思而少于陈安卿。”陈普对本书颇为自信,认为乃入道之门,可助学者登堂入室。其门人余沙认为,该书较之程、陈之作,不仅篇幅上详略得中,而且在确立字义名目、辨析字义含义上更显精密。②
陈普认为字义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圣贤已逝,道存文中,文由字成,故字义之是否明晰,直接影响对圣人之道是领悟还是背离,继而影响为学效用是专精贯通还是鲁莽灭裂。对字义之慎思明辨,乃笃行工夫之前提,不可忽视。在该书自序中,他反复强调性命道德等字义对六经四书具有纲领、灵魂的意义,学习作为六经四书之精华的字义,是进入经书要领所在,决定了能否明乎大道,领悟圣贤之心。对于明道成圣而言,具有门户和唤醒的功能,是必由之径。此显示出陈普对字义学有着自觉认同和高度评价。
明于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字之义,则六经四书之全体可得而言矣。世之知书而或不明于道,不得于圣贤之心者,未明于此等字义故也。明于此等字义,则千门万户以渐开辟,当如寐之得醒矣。③
陈普清醒认识到字义的复杂性,提出“字一而义不同”说。字有其最初本义,亦有其后来之引申义,本义与引申义又有着内在联系。以“道”为例,本义共由之路与引申义之间,距离看似很远,其实仍有迹可循。“一字一义,有一字而数义者……其义之相去若甚远而究其终,皆同出也。”①他很关注“字”的语境义,如指出“安”在不同语境中具不同含义,“恭而安”、安行之安乃是“不思不勉而自无不合道之安,圣人之事也。”安土、静而后能安之安乃是“乐天知命之安,圣贤之所同”。安其身、利用安身,乃“不愧不怍,无过无罪之安”。并指出“静而后能安”,据朱子“无所择于地”解当与“安土之安”同义,学者理解多误。鉴于字义“不可以一二名”的特点,该书尤留意字义的细微区别,此为该书特色之一。
该书特色之二是设立了“人”“物”“止”“一”等某些较为新颖的范畴,如专立“人”范畴,指出人得天地生物之心而为心,进而从三才之道的立场推出人由此为天地之心,居三才之中。正因“人”内在的具备仁,故与仁同音,孟子“仁者人也”说即表明作为恻隐之心的仁充溢表现于人之体内,以突出人、仁的一体性。如“物”范畴,认为其意为“实也。天地间万物万事皆道之实体也。理之所有而不可无者也。”以“实”解“物”,比较罕见。
该书特色之三在于以“公私”“理”“诚”作为核心范畴贯穿全书。如“诚”的诠释,其基本义为真实,“诚,真实也。”与《北溪字义》强调“无妄”不同,陈普突出了“不杂”,指出诚“全体皆天道”,是天道的呈现,“不杂”表现在两方面:不杂他道异端,不杂外物。“全体皆天道而无他道外物之杂也。杂他道外物则为伪妄而害其体。”②如掺杂他道外物,则是虚伪胡乱,将伤害天道诚体,必须消除之方为真实。陈氏立论当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鉴于现实生活中学者用功不纯之学弊而发,二是针对学者惑于异端之学而发,强调诚者天道,天道乃是最真实无虚纯粹不杂者,非天道者则为虚伪妄乱,背离了诚。明白诚的天道意义,则可以辟除异端而不为所惑,这一思想与程子“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说有关。在“一”的阐释中,他继续强调“诚”的纯杂之辨,“所谓一以贯之之一,诚者之事也。去其杂以纯其体,防其间断而常久其功,此则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诚之者之事”①。一贯之一表达的是诚者始终保持于纯粹无杂之境界,精一、克一、主一乃是强调当如何去其杂质以纯其诚体,并持之以恒的诚之工夫。他称赞蔡沉“不杂之谓一、不息之谓一”解“最尽”。不杂、不息正是从纯一不杂的角度解诚。此当本于《中庸》“为物不二”、程子“一心之谓诚”、朱子“一于善”说。此外,陈普在对信、虚、实、名、实等范畴的诠释皆以“诚”相释,可见“诚”之枢纽地位。
勇于批判理学前辈之说是该书另一特色。陈普对作为理学“字义”源头的朱子《四书集注》即有不满。认为朱子对《告子》上篇的注释在本意与文义的处理上存在问题,一是本意不对而文义对,如“生之谓性”注。二是本意对而文义不安。如注中所引程子“才禀于气”说。并指出《集注》“朋来之乐”取程子说,将之与“不知不愠”合而为一,仅仅看到二者在同一章内皆阐发“乐”这一范畴,而没有察觉“字一而义不同”,“乐”具有差异性与层次性,不愠为深层次的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乃是较低些的乐。
文公以朋来之乐与不知不愠用程子说,合为一于注之末。盖只缘章内一字为注。其实,朋来之乐犹浅,不知不愠始深。不知不愠即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亦渐有意耳。②
陈普把另一批判矛头指向《北溪字义》,认为它同样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某些字义的阐释不准确。如关于“极”字后段采用己说处多有不妥。二是收字范围太过狭窄,影响了广度。如“三才”丝毫未提及。据此看来,陈普似乎有意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陈淳。“北溪陈安卿《字义》用文公之说已善,而后段说‘极’字多未当,盖亦未深明也。至于‘三才’则未闻有一语及之者。”③
总之,陈普《字义》晚于《北溪字义》,体现了“字义”学的某些发展。在范畴选择上,设立了不少有特色的新范畴。同时对某些核心范畴如诚、理、太极等的诠释颇见特色,多少体现了字义学的发展。虽总体上无法与《北溪字义》之严密性、精确性、学术性相提并论,但多少摆脱了“浅陋粗糙”的蒙学性,可谓介于蒙学与学术性著作之间。
四 “字义”之变异:《西山读书记》与《四书通旨》
《北溪字义》奠定了“字义”体之典范样式。继此而作者,则将“字义”与其他体裁相结合,形成了“字义”的变异体。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朱公迁《四书通旨》即为此类。二书共同特点是:以若干范畴(“字”)为纲,以四书材料为目来组织全书,此以数十范畴组织四书之形式,可谓类聚。此类聚体现了范畴优先的立场,具有“字义”体特征,类聚之范畴又多源于《四书》,可视为诠释《四书》之作。二书差别在于:《读书记》采用“字义”、《四书》原文(亦有非《四书》者)、注疏的“三合一”形式,为“字义”+注疏的综合;《通旨》则采用“字义”、《四书》原文、辨析的形式,为“字义”+经疑的综合。
(一)《读书记》的“字义注疏体”
此一体裁以传统注疏为主体,除首列一范畴统领相应材料外,其余则纯为注疏形式。先列含所列范畴的四书(或五经)相关原文(或节选),再大量引用程、朱学派之说,间或在按语中表达个人见解。此字义+注疏的综合式,字义起统领作用,经典文本被拆解、打乱、截取,服从于范畴的需要。注疏则摒除了文字音韵训诂、纯任义理,体现了义理解经的特征。所引各家说颇为繁复,不乏相互对立者,目的是为了提供丰富、多样的解说,予读者以思考、抉择的空间。但这种材料的丰富、复杂却让初学者易陷于其中而难以得其要领。故该书并非为初学之教材。此外,该书“理学经典化”意识强烈,常将濂溪、二程、张载等重要论说作为与经文同等的正文形式直接列出,如“性即理也”,《西铭》等,以示理学家论述具有与元典同等之地位。
西山创造出此种字义加注疏的综合体,欲在吸收二者之长而避其短。“字义”体的优长是简明扼要,给范畴以教科书、字典般的解说,缺点是不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想象、理解、选择的空间,易受编纂者思想的限制。又由于它摆脱了训诂、文本,实质上摆脱了字义的历史、思想、文化语境,易给学者枯燥乏味、悬空脱节的感觉。故“字义”只是理解程朱《四书》的阶梯,并不能代替对《四书》和程朱著作的研读。西山在“字义”基础上辅以原典、注释,用意即在于落实陈淳“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理念,避免纯粹字义体的局限。反之,注疏体以材料丰富、解释详尽著称,然其繁琐之弊亦不可免。将二者结合之,则能收取长补短之效。
朱子对类聚言仁颇有疑虑,西山对“字义”亦抱同感。故《读书记》“仁”卷之末特意引朱子、南轩关于类聚言仁的讨论,南轩秉程子类聚观仁的想法,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则担心此种做法会形成贪图捷径的心理,产生口耳之学的弊病,加剧学界盛行的“厌烦就简、避迂求捷”的学风,要求南轩以序的形式将此忧虑告诫之心布告天下,或将二人关于讨论此事的往返书信作为书的附录。南轩接受了朱子的看法,“悉载其语于卷首。”西山指出,朱、张二先生为学者考虑深远周到,今《读书记》以字义为纲领,辑合相关文本,恐亦有前贤所虑之病,故载其说于此自我警示。“二先生之为学者虑也至矣。今类辑此编,亦恐有如二先生所虑者,故书之篇末以自警。”①
《读书记》与《北溪字义》皆为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栎曾加以比较论述。他说:
《读书记》一书既博且精,凡诸经、诸子、诸史、诸儒之书之所当读当讲者,皆在焉,乃有载籍以来,奇伟未尝有之书也。……《读书记》尤博大精微,可以该彼二书,而彼二书不能该此一书也。②
陈栎对陈淳有很高评价,赞他为“朱门第一人”,赞《字义》“玲珑精透”、兼具简明通俗、高妙精要、贯通上下的双重性。但他对《读书记》评价更高,认为该书广博精深,完全可以包括《增广性理字训》、《北溪字义》,实为自古以来罕有的“奇特伟大”之书,为传圣贤之道的不朽之作。就广博和深厚论,《读书记》当优于《北溪字义》。
(二)《四书通旨》的“字义经疑体”
《四书通旨》与《读书记》所异者在于该书纯以98个字义类聚四书原文而不带任何注释,仅在所类聚文本后,对文中范畴之义略加异同辨析,近乎元代科场流行的“经疑”体,可谓“字义”与“经疑”的结合。其最大特点是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字义、义项、含义、文本的四级含摄方式,以“凡……皆此类”“凡几见”等术语把四书文本重新归为98类,实现了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具体而言,每门字义分为若干不同义项,采用“皆是此类”“与此类同”等以义归类的方式将文本安顿在各具体义项下,以此区别范畴之同与具体义项之异。同一义项下又析出若干含义,聚合若干文本,著者对各文本含义的细微差别作简要辨析。通过这种四层分析含摄的方式,最终落实到具体文本,达到通《四书》之旨的目的。《四库总目提要》对其特点有简要概括:“是编之例,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①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较,该书最大程度实现了范畴与《四书》文本的一体化,全部范畴皆来自四书文本,它书所收太极、皇极、天理等因在《四书》外,皆未被收入。《通旨》对范畴与文本关系的处理尚另有一特点,即某一具体文本中虽无某“字”,却可从思想上将其归入该“字”下,显示出思想判定优先的立场。如“上天之载”一条并无“敬”字,却列为“敬”范畴之“持敬之功该动静贯始终兼入德成德”义项下。②
元代科考采用“经疑”问答形式考查学子对朱子四书的理解,着重文本的异同比较,疑似辨析,融会贯通。此一出题特色非常吻合“字义”体。《通旨》虽非科考经疑著作,然对《四书》异同的疏通辨析,带有鲜明的“经疑”色彩,辨析之语如轻重、要领、对反、表里、发明、统言专言、兼言泛言、凡几、偏全等为“经疑”所常用。
《读书记》、《通旨》非标准之“字义”体,除综合性外,二书“字义”之选取并非以纯粹范畴为主,而注重经书的类聚与工夫、事项的大致分类,《读书记》以五经四书之名分列字义,设立《大学》、《广大学》、《易指要》、《书指要》等“字义”,《通旨》则以人物列为字义,设立孔子、子思、孟子等,约有40门“字义”纯为事类,故被讥为“体近类书,无所发明”。较蒙学类“字义”之粗陋,二书略有“微嫌其繁”,不够简洁切要之弊。此外,二书皆不对任何范畴作具体解释,而依次罗列它在各文本中的具体意义,《读书记》尚列出各家注释阐发,《通旨》则特重异同辨析,这是此类著作异于纯“字义”类的又一特色。在注释宗旨上,二书亦不以童蒙教化或编撰简要之教材为宗旨,而是以提供阅读思考之文本,锻炼读者思辨能力为追求。故《西山记》常采用朱子、南轩不同说法,以“读者详之”的案语引导读者加以辨别。
上述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自一传至五传的六部“字义”著作,形成了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模式:“字义体”,是朱子学者对中国范畴之学的贡献,体现出朱子学者的传承与创新。此类著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首先,皆“摆落章句、独崇义理”,放弃了对经典文本的事实性考证,直接以简洁明了的“字义”形式传达对程朱理学的准确理解。无论是大到著述理念,小到具体字义,其论述视域皆不离程朱思想,理气、心性、工夫居核心地位。其次,字义的选取基本源于朱子《四书》,又落实于此书,这是字义体的又一基本特征。朱子四书为朱子一生心血所萃,门人后学以不同形式对之阐发,“字义体”即是门人后学创造出的新形式,它对推动朱子《四书集注》成为理学最重要的经典,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又次,在“字义”阐释形式上,朱子门人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的著述形态,体现为从理学蒙书、理学辞典至理学精华的三次转变。其定位亦发生了蒙学教材、字义模板到四书参考的变化。最后,在“字义”的具体诠释上,门人后学尽管皆以忠实阐发程朱思想为追求,但他们并不忌讳对程朱及前辈的不同看法,而是大胆提出批评和异议,体现出勇于创新的朱子学精神。
“字义体”作为对理学四书的专题阐释,其指导思想当源于朱子的童蒙教化,理论核心来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其类聚范畴的形式当源于程子的“类聚言仁”说,但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与朱子的理念相偏离的,首先是孤立的抽离若干范畴加以训释,背离了虚心涵咏本文的理念。其次,对文本的阐发放弃了文字义的考察、抛弃了朱子非常看重的章句训诂之学。这样得出的义理,朱子恐怕是不放心的。真西山试图将字义与传统注释体结合起来,即是为了矫正字义体的干枯、单薄之弊。客观而论,“字义体”作为研究、阐释理学、四书的一种特有形式,对宋明理学的发展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亦比较有限。
总之,朱子门人后学将理学范畴与四书诠释相结合所创造的“字义体”,从形式和内容上皆对理学范畴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诠释,是对朱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使得理学与四书进一步融为一体,四书几乎成了理学的专属,理学亦借助四书而得到更合法广泛的传播。深入研究理学“字义”,对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理学研究、四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节 勉斋《中庸》学对朱子的接续与发展
朱子《中庸章句》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庸》诠释系统,主导了后世的中庸学发展。其高弟黄榦以创新之精神,在《中庸》章节之分、义理建构、工夫系统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赞为“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①勉斋将《中庸》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指出道之体用乃贯穿全书之主线,提炼出以戒惧慎独、知仁勇、诚为脉络的《中庸》工夫论系统,并深刻影响了弟子饶鲁、后学吴澄的中庸学,形成了《中庸》学上独树一帜的勉斋学派。富有开创性的勉斋《中庸》学虽寂然无闻,然其上接朱子,下开饶、吴,对宋元朱子学的《中庸》诠释实具继往开来之意义。
一 章节之分
勉斋据自身对《中庸》的理解,对《中庸章句》的章节之分做出了调整,朱子章句分《中庸》为三十三章,三大节。勉斋提出应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他的《读中庸纲领》(小字:分六段授陈师复)详细阐述了他的想法(引文括号中文字为笔者所加):
(第一节)天命之谓性止万物育焉。此一篇之纲领。(1章)
(第二节)仲尼曰止圣者能之。此《中庸》明道之体段,惟有知仁勇之德者为足以尽之。(2—11章)
(第三节)君子之道费而隐,止十九章之半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言中庸之道无所不在,无时不然。(12—20章半。按:十九应为二十之误,“不明乎善”属20章“哀公问政”。如勉斋认为该章当为19章,应有所交代、提示。)
(第四节)诚者天之道也止纯亦不已。道皆实理,人惟诚实足以尽道。至此,《中庸》一篇之义尽矣。(20章下—26章。据勉斋“十九章之半”说,他把“哀公问政”章分割为上、下章,分属于第三、四节,可见他此处较《章句》多分出一章,即21—27章。)
(第五节)大哉圣人之道止孰能知之。此后六章,总括上文。一篇(疑为“节”之误)之义以明道之大小,无所不该,惟德之大小,无所不尽者,为足以体之。中间“仲尼祖述尧舜”,再提起头说,仲尼一章,言大德小德无所不尽者,惟孔子足以当之。此子思所以明道统之正传,以尊孔子也。至圣者,至诚之成功,至诚者,至圣之实德,此又承上文称仲尼而赞咏之也。(27—32章,即28—33章。)
(第六节)《诗》云“衣锦尚絅”止无声无臭至矣。末章言人之体道,先于务实,而务实之功有浅有深,必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息”而后已,至此,则所谓“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之谓也。(33章,即34章)①
可以看出,勉斋对《中庸》前三节的理解基本同于朱子。朱子对首章的阐发受到勉斋的推崇,《章句》引杨时说指出首章为“一篇之体要”,勉斋亦以“一篇之纲领”述之,认为此章言简意赅,包括本原、工夫、效验三方面,“此一章字数不多而义理本原,工夫次第,与夫效验之大,无不该备。”②勉斋对第二大节看法亦与《章句》基本相同,《章句》认为本节主旨是知仁勇三达德,“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余见第二十章”。①勉斋对第三节的看法亦与《章句》同,认为本节阐明了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费隐章对道的存在流行作出了极其显著的揭示,学者于此对道应当有所领悟,否则即是为文义所束缚,而无法见道。“看《中庸》到此一章,若无所见,则亦不足以为道矣。充塞天地间,无非是理,无一毫空阙,无一息间断,是非拘牵文义者之所能识也。”②《章句》亦认为本章主旨是阐发道之流行,呼应首章道不可离,统领以下八章。“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③
勉斋分章与朱子最大不同是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朱子认为,本章内容丰富,实为承上启下之章。上承前舜文武周公数章,阐明圣贤所传道统的一致性,对诚的论述则下启此后各章主题,故本章所述具有某种综合性,兼道之体用、大小,以呼应本节之费隐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举而措之,亦犹是耳。盖包费隐、兼小大,以终十二章之意。章内语‘诚’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④尽管朱子特别提到本章所论之诚,乃全篇枢纽,下文皆以诚为重点,但他仍然认为,对诚的阐发亦当置于道的背景下,没有必要单独突出、独立。这一点勉斋与之不同。本章历来是《中庸》诠释争议的焦点,朱子当时即因此与吕祖谦、南轩等往返辩难,朱子去世后,承担传道重任的勉斋仍在此问题上产生异议,可见勉斋“不唯朱子是从”的为学态度。勉斋对此章亦抱有极高评价:
哀公问政一章,当一部《大学》,须着反复看,榦旧时看,越看越好。⑤
此章语极宏博,其间语意若不相接,而实伦理贯通,善读者当细心以求之,求之既得,则当优游玩味,使心理相涵。则大而天下国家,近而一身,无不晓然见其施为之次第矣。①
勉斋将本章与最为朱子重视,被视为整个儒学纲领的《大学》相比,认为其内涵丰富,义理精密,深厚含蓄,故须反复熟读体会,方能见出其义理无穷。就本章文本论,其用语广大,所论话题似乎时有跳跃,缺乏内在的连续整体性,但其内在思想则明畅条达,精密有序而互为贯通。故须以精细之心来探究之,在求得内在文义基础上,再从容涵养、反复把玩,体会咀嚼其味,最终达到心理相涵,融化为一的境界,如此则可进乎内圣外王之道。勉斋所强调的是,本章不仅阐释了明德修身之方,而且论述了新民治国平天下之道,义理无穷,足与整部《大学》相比。
勉斋将本章划分为上下两章,且分别归属第三、四部分,其用意很明显,就是突出“诚”的地位。下章自“诚者天之道”始,与“诚明”“至诚尽性”“曲能有诚”“至诚如神”“不诚无物”“至诚不息”章构成了以诚为中心的第四部分。他认为《中庸》一书,至此为止,其意义已经穷尽。“至此《中庸》一篇之义尽矣”。也就意味着,在前面分别论述一篇纲领、三达德明道之体段、费隐明道之普遍存在后,至“诚以尽道”,乃是《中庸》全部意义所在。
在大节之分上,勉斋与朱子最大不同在于是否将诚独立为一个单元。《章句》视哀公问政章为一个整体,归于费隐节。自诚明章以后直至篇末,统为一大节,其主旨乃是天道、人道,“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②。这种安排显然并没有特意突出“诚”而是强调了“道”,认为诚内在于天道人道中,乃是道的应有之义。这亦表明朱子是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中庸》全书的,自有其合理性,在《中庸》是一篇还是两篇的质疑中,这种安排很好地保持了《中庸》一书的内在完整性和一体性。①
勉斋以六章篇幅构成以“诚”为主的第四节后,又将“大哉圣人之道”以下六章划为第五节,这亦与朱子不同。勉斋认为本节与上节关系密切,是对上节诚论的总结概括,是论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只有穷尽德之大小,无所不至者方能体道,乃是围绕道、德两个概念展开。前三章是论道之大小,后三章以仲尼为例论证德之大小,与天相合,《章句》则认为前三章是人道,后三章是天道。
勉斋将最后一章独立为一节,引《诗》论述体道工夫及其高远境界。本节与首节独立与否并不对全书结构产生大的影响,故很多朱子学者亦倾向于将首、尾两节独立出来。勉斋曾对《中庸》下半段关系有一整体论述: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间又怕人做得不实,“诚者天之道”以后,故教之以“诚”。后面说“天下之至圣”,是说其人之地位,“至诚”是说其人之实德,到“衣锦尚絅”以后,又归“天命之谓性”处,此四段最好看。②
勉斋认为,《中庸》前面是有关工夫论的讨论,如三达德等,接着费隐一节又担心人工夫实践不真实,故自哀公问政章的“诚者天之道”后,开始论“诚”。天下至圣、至诚章分别论述圣人之地位和德性,末一章则重新呼应首章“天命谓性”说。可见,在勉斋看来,《中庸》以论诚为界限,似乎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面以戒惧慎独、三达德工夫为中心,包括第一、二、三节;后面以诚的境界为中心,包括第四、五、六节,而他认为自“诚”论一节后,“《中庸》一篇大义尽矣”,正表明此意。
二 道之体用《读中庸纲领》对各节的概括显出勉斋从道的角度论述中庸。如第一节言道之纲领,第二节“明道之体段”,第三节言中庸之道无所不在、无时不然,第四节论“道皆实理,人惟诚实足以尽道”,第五节明道之大小,第六节言人体道之境界。勉斋曾讨论学习《中庸》的方法,他以程子、朱子说为基础,得出以体用论中庸之道的思想。在《中庸总论》中给予了详尽阐发:
苟从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先生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①
《中庸》一书具有不同于《论》、《孟》的特点,故从总体上通晓全篇旨意,较之具体的章句分析更为重要,程子理事说、朱子诚之枢纽说,精密、确切的点出了全篇要旨,是学习《中庸》之指南。勉斋由此进一步提出道之体用说:
窃谓此书皆言道之体用、下学而上达、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与道,则性为体,而道为用矣;次言中与和,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矣;又言中庸,则合体用而言,无适而非中庸也。又言费与隐,则分体用而言,隐为体,费为用也。自‘道不远人’以下,则皆指用以明体;自言诚以下,则皆因体以明用。大哉圣人之道一章,总言道之体用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之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尽道之体用也,大德敦化,道之体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用即体,体即用,造道之极致也。虽皆以体用为言,然首章则言道之在天,由体以见于用,末章则言人之适道,由用而归于体也。②
首先,《中庸》全书皆围绕道的体用展开,体用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书中很多重要概念即具有体用相对关系,如性与道、中与和、费隐,中庸则体用兼具。全书文本结构的内在联系亦为体用关系,如“道不远人”章以下,是“指用以明体”,“言诚以下”则反过来,“因体以明用。”此是受《章句》影响,朱子认为“道不远人”章所论,“皆费也,而其所以然者,则至隐存焉。”“诚则明”章是论述天道、人道,此后12章,皆反复交错论及天道、人道这一主题。但勉斋不认同此说,《章句》认为“大哉圣人之道”章是“言人道”,勉斋指出是总言体用;对认为是言天道的仲尼祖述及以下至圣、至诚章,勉斋则认为仲尼祖述章是言圣人尽道之体用,至圣、至诚则是分别全道之用、道之体。勉斋还认为,末章是论体用为一的最高境界,首章命性之说,是由天到人、由体及用,末章则是由下学上达,以人达道,由用归于体。二者首末恰相呼应,体现了体用概念对全书的贯穿始终。
其次,分析《中庸》论道之体用的四个原因。
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知道有体用,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知道之有体,则凡术数词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则虚无寂灭,非道也;知体用为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体用合一,则从容中道,皆无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①
如果知道有体用两面,则可以实现日常动静之间,达到自然纯乎天理而人为私欲的境界;则可以辨析小道、异端之学的不足,或有用无体、或有体无用。一方面,既知道之体用是有分别的,则须始终于操存省察之上用功;又知道之体用又是合一的,体即用、用即体,故有自然从容的中道境界。中庸以体用论道,实现了对道的最高论述。既然如此,为何孔孟不言体用而子思言之?孔孟何为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学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体,恕即用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非道之体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传之子思也。孟子曰……恻隐羞恶辞辞逊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传之孟子也。道丧千载,濓溪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其言太极者,道之体也;其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道之用也。……圣贤言道,又安有异指乎!①
勉斋就孔曾思孟周子的道统传承立场论述了道之体用。曾子得自孔子的忠恕,即道之体用,“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曾子传给子思的道之体用,孟子四端说是得自子思的道之体用。道丧千年之后,濂溪以太极、阴阳说重新接续道之体用说。可见,道之体用为儒道之核心内容,是一直传衍不息的。
勉斋进而解释了三个问题,一是天人体用的分合关系。
或曰:以性为体,则属乎人矣。子思……乃合天人为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②
勉斋以太极说来解释之。指出性来自天,是理、体,同时又为人禀受,则转为人之用。天人无间,人所具有者本源于天,统体于太极,天下万物皆在性理之内。反之,万物各具一太极,故在天者,同时又内在于人,此为天人合一、体用一如也。
二是体用之分与程子性气、道器之合的冲突。或曰《中庸》言体用,既分为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气、气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则何以别其为体用乎?曰:程子有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也”。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类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色、天性之谓是也。①
勉斋以程子体用一源说进行解答,指出分合不同之解,乃是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故当灵活观之,其中并无不合。从理的角度论,则体始终包有用,并未脱离用而独立存在之体,如程子冲漠森然之说即是此意。从物的角度言,则用始终内在具有体,没有脱离体的用,如《易》之阴阳即是道,《孟子》形色即天性说,即是指出体用之合。
其三,既然体用不离,又如何区别费隐?
如此,则体用既不相离,何以别其为费为隐乎?道之见于用者,费也;其所以为是用者,隐也。费,犹木之华叶可见者也,隐,犹华叶之有生理不可见者也。小德之川流,费也;大德之敦化,隐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体用之未尝相离也。嘉定戊寅栖贤寺书此,以为《中庸》总论。②
勉斋指出,费为道之发用,隐为用之根源。费是显现于外的可见之花叶,隐是潜伏于内无法目睹的生生之理,此见体用二者有别。大德敦化与小德川流分别为隐、费,但又互相包容,彼此相涵,可见体用又未尝相离。勉斋不仅以体用为中庸之道的根本,而且视为他对儒家之道的根本体悟,反复以之来详尽剖析《中庸》。他在《复叶味道》书中说:
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间只是一个道理也。①
道在天下的呈现,无非是体用而已。体只有一个,用则是无数,体用是一多关系,是理一分殊。《中庸》开篇性道即是一本万殊关系,大德与小德亦然。他将之与朱子的《太极图说解》紧密结合,语大是一本万殊的万物统体太极,表明性外无物;语小是万殊一本的一物各具太极,指性无不在。从性的普遍视野看,万物皆同,正因万物之理皆同,故只要存心、把握住固有良心,则事物之理无不具备,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义。自道的分殊角度,万物各异,故需要事事逐一穷理,以达到万物之理的贯通。故圣贤或就道之体的理一言,或就道之发用的分殊言,说虽不同,义则为一,皆言道之体用也,此乃为世界普遍共有之理。
勉斋对体用说的论述是以朱子《太极图说解》的“统体太极、各具太极”说为基础的,由此悟出体用的分合、兼统关系、他指出当以朱子太极统体各具说与《中庸》尊德性、道问学注比照合观,一方面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各自兼有体用,但二者之间却是统体为体,各具为用。语大、语小虽然皆是指用,但二者当以语大为用。天命谓性与率性谓道、大德与小德关系亦是如此。可见体用是相对言的,有自身之分体用,又有以相关对象相较的体用。更取朱先生《太极图解》以“统体太极为天下无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极为性无不在”之语,并《中庸》尊德性道问学注观之,不知如何?……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底又是体,各具底又是用。有统体底太极,则做出各具底太极。①
三 “戒惧慎独知仁勇诚,此八字,括尽《中庸》大旨”
在《中庸总论》中论述道之体用时,勉斋即提出求道工夫的问题,他认为戒惧慎独、知仁勇、诚八字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工夫,也是全书大旨所在。“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巳,是则一篇之大旨也。”②为此,他专门撰有《中庸续说》一文论述之。
至于学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复包罗而极其详且切焉。……首言戒惧谨独,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无不善者而为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简而易行,学者于此而持循焉,则吾之固有而无不善者,将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末言诚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见天下之理无不实,欲人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③
子思对如何用功,反复论述,极其详尽切当。首章提出戒惧慎独工夫,针对性、道本为人所固有而纯善无恶,故工夫在于防止未然之不善的侵蚀而审察所以然,此工夫具有易简特点,只是自然而发的当下一念。“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实质是静时存养、动时审察的动静不离工夫,以此实现性道的当身存在。知仁勇三达德,乃针对克除气禀、物欲而发,需要明知、力行、勇猛工夫,以保持固有之善,实质是知行并进工夫,以做到由体至用的展开,皆合乎中庸。最后言诚,针对天道、人道之分,天理本是真实无妄的,故人当真实用功,以保全真实无妄之天理。它始于择善固执工夫,终于无声无臭。
勉斋认为,《中庸》对此八字工夫有着详切论述。
戒惧谨独者,静存动察之功。能若是,则吾之具是性而体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则由性以达夫道者,举合乎中庸而无过不及之差也。曰诚者,则由人以进夫天,圣贤之极致也。是非其言之极其详乎。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谨独于至微至隐之中,则所谓静存动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继之以仁,曰仁矣而继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则所谓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诚也,本于择善、固执之始,而成于无声无臭之极,盖至于所谓大而化之,过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岂非又极其切者乎。若不极其详,则学者用心或安于偏见;不极其切,则学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忧虑天下后世而为是书也。①
戒慎工夫的实质是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如能做到此,则能实现天命之性、体验率性之道。知仁勇则是知止力行工夫,如能做到此知行工夫,则由天命之性落实于率性之道过程中的种种行为,皆能合乎中庸之道。诚则是下学上达、由人而天的圣贤最高境界,即此已显出《中庸》论述之详尽。“戒慎不睹不闻、谨慎至微至隐”显出静存动察工夫之紧切;言知而紧接以仁、勇,可见致知力行工夫之紧切;言诚而始终于择善固执、无声无臭,又见其紧切。之所以如此详细紧切,是为了防止学者安于偏见、止于小成。此八字工夫事关道之传承,故对之加以极切阐释,就成为子思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勉斋反复指出,此三节八字工夫次序丝毫不可紊乱,先是戒惧,其次知仁勇,最后是诚,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始于戒慎,紧接的知仁勇则是对戒惧的实行,知仁勇又需要守住其诚来加以落实。但反过来讲亦然,戒惧的实行须先之以知仁勇,知仁勇的实行又以诚为前提,故最终又落实于戒惧慎独。工夫可谓终始于戒惧。
始之以戒惧谨独,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终之以诚之一字。①
《中庸》一书,第一是戒谨恐惧,然戒谨恐惧亦须是先有知仁勇以行之,然知仁勇固所以行之,又须是守之以诚后可,其终又归于戒谨恐惧。此《中庸》之大略也。②
戒惧可谓三节工夫之核心,对此工夫时刻不可离开,是工夫主干所在,知仁勇是具体做知行工夫,包括读书穷理,诚是对工夫的最后实现,有此则工夫完满无遗,它兼有工夫与形上义,尤其是全书后面,至诚诸说的形上境界义极其突出。如上文所引,勉斋认为全书至第四节“诚”论,已穷尽一篇之义,即居于此工夫论立场而发。“《中庸》戒惧慎独是大骨,顷刻不可忘,知仁勇是做工夫,读书讲明义理,后面着个‘诚’字锁尽。”③
在给饶鲁的信中,勉斋对此八字评价更高,认为不仅是《中庸》大旨所在,更是囊括穷尽了千古以来圣贤的教法。
《中庸》之书首言戒惧谨独,次言智仁勇,终之以诚,此数字括尽千古圣贤所以教人之旨。戒惧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谓也;谨独以致乎和者,集义之谓也;致中和,岂非检点身心之谓乎。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过求所以致夫中和也。如此而加之以诚,则真知实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学者立心,便当以持养省察为主,至于讲学穷理,而持养省察之意未尝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义愈精矣。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皆务外者也。①
勉斋从两方面来论证此点:其一,将戒惧、慎独与致中和、居敬、集义等重要工夫对应起来,戒惧是居敬,是致中工夫、慎独是集义,是致和工夫,故致中和不过是检点身心之学。知、仁、勇则是达到致中和的途径,于此基础上再贯注以诚,则能做到真知实行、勇猛不懈。居敬是把持养护此心,集义是反省审察此心,故此八字工夫无非是持养省察、检点身心。其次,将戒慎工夫与讲学穷理比较论之,强调为学当以戒慎存养省察为主。如上所述,戒慎是八字工夫“大骨”,故常以之为工夫代表。为学以戒慎还是讲学为主,直接关系到为学方向是切己向内还是务外为人。勉斋直接批评了凡是不以戒慎为工夫之主而只知讲学穷理者,皆是务外之学。因戒惧慎独终身事业,故不可有丝毫放松,讲学穷理不过是讲明道理使之不误而已,并未进入到实践层面,只能起到工夫的辅助作用,“须是如中庸之旨,戒惧谨独为终身事业,不可须?废,而讲学穷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勉斋以戒慎、知仁勇、诚作为工夫要领,一方面是在《章句》影响下提出的,如静存动察来自《章句》“存养省察”说,认为自“君子之中庸”章开始言知仁勇,诚字因天道、人道之分,皆来自《章句》说。朱子认为从诚明章开始以下十二章,皆是自天道、人道反复论说。另一方面,又是勉斋的独特体会和创新,通过对戒慎、知仁勇、诚的三项工夫的突出,使得原本以形上学、深奥著称的《中庸》有了一条非常简洁清晰的工夫线索,是对朱子《中庸》工夫论的概括和提升,也是对《中庸》诠释的重要补充与深化。
四 双峰、草庐对勉斋中庸学之传承
勉斋中庸学确有“发朱子之所未发”处,并深刻影响到后世朱子学。其弟子饶双峰、双峰再传吴草庐亦皆对之作了新的继承阐发。总体看来,双峰受勉斋的影响很明显,二者可谓大同小异,但这小异却影响甚大。
在章的划分上,双峰亦将全书划分为34章,亦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但在具体划分上却与勉斋有所不同,他根据“哀公问政”至“不可以不知天”为孔子之言的依据,将之划为一章,即第20章;自“天下之达道”至章末“虽柔必强”是子思推衍孔子之意所成文字,另划为一章,即21章。深受双峰影响的草庐在《中庸纲领》中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干脆将哀公问政章拆分为四章,并独立为一节,刻意突出该节的特殊地位,其主旨为“论治国之道在人以行其教”而非诚。在大节的划分上,双峰与勉斋亦有同有异。同者,皆分为六节,皆将第四节单列为诚,差别仅在于对哀公问政章的处理,双峰尽管亦一分为二,却皆归入第四节“诚”论,勉斋则分别归于三、四节,如此,本节双峰较勉斋多出“哀公问政”一部分。在各节主旨及其关系认识上,双峰颇有创见。他以简明扼要之语概括了各章要旨:首章中和节,2—11章的中庸节,12—19章的费隐节,20—28章的诚节,28—33章的大德小德节,末章的中和节。特别是指出全书是一个具有高度联系的有机整体,各节之间彼此照应,首、末两章皆自成一节,中间四节则是两次开合。第一次开合是由中和而中庸而费隐的打开,再由费隐而诚的闭合。第二次开合是由诚而至道至德的放开,再由至道至德到末节无声无臭的合拢。两次井然有序的开合显示了《中庸》结构的完整性和节奏性。①双峰之六节说影响盖过勉斋,得到后世主流朱子学者的认同,而勉斋之说几乎湮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恐与双峰对各章节关系的精密论述有极大关联。②
如果说双峰是在勉斋基础上“后出转精”,那么草庐则显然更有针对双峰的意味,他受双峰思想深刻影响是无疑的,数次提及对双峰《大学》、《中庸》的看法,批评双峰章句说过于分析。他在《中庸纲领》中将全书分为七节34章,在章的划分上,他对朱子《章句》采用了合并、拆分法,颇不同于前人。把《章句》22章“唯天下至诚尽性”与23章“其次致曲有诚”合为一章,构成他的25章;把“不诚无物”章与“至诚无息”章之“故至诚无息”至“无为而成”部分结合起来组成他的27章,而“至诚无息”章剩下部分“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以下则单独组成28章。在节的划分上,除将哀公问政章独立为一节,首节、次节、第3节、第七节与前人相同,差异在于把24—30章划分为明诚、圣天一节,突出“诚”在全书中的中心地位。且把31、32、33章划为第六节,论孔圣之德与天为一。列简表如下:勉斋、双峰20/21章为朱子《章句》20章哀公问政章之拆分,具体所分有所不同;草庐一行,括号中为朱子《章句》之分,但草庐四、五节的各章之分已与朱子不同。①
关于《中庸》主旨,勉斋认为《中庸》是论道之书,尤其阐发了道之体用说,双峰亦明确提出,“《中庸》一书大抵是说道”,突出了中庸之道与物不杂不离的双重特点。勉斋对《中庸》三项工夫的阐发,在双峰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回应和阐发,双峰认同朱子、勉斋的戒慎解,“戒惧,存养之事”“慎独,省察之事”,但亦有新的理解,对《章句》颇有批评。特别突出了第二节“中庸”节所体现的变化气质的自修工夫,突出了知、仁、勇的重要性,认为“《中庸》大抵以三达德为体道之要”①。饶鲁认为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五句当以首句为纲,其余四句为目,皆言道问学之事,提出了尊德性在其中的主干地位,还提出了“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这一带有浓重心学意味的命题。②这一看法得到草庐的认同,并获得进一步弘扬,草庐强调以尊德性为主体的情况下来展开道问学,力求兼顾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尊德性为体,道问学为用,二者具有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并由此被视为元代朱陆合流的代表。③
综上所述,勉斋在《中庸》分章、主旨、工夫论方面皆对朱子《章句》有所改造和突破,形成了自成一派的《中庸》学,并得到后学双峰、草庐的进一步推阐,尤其是双峰的章节之分,更是成为后世理学中有代表性的见解,显示出勉斋学派的创新能力。元人程钜夫已经道出此点,他说,“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双峰之说,又有勉斋所未及者。”令人奇怪和遗憾的是,双峰、草庐的《中庸》学皆有相当之影响,作为二者源头的勉斋《中庸》反而默默无闻,不为学界所熟知,一冷一热适成对比。勉斋著作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属《论语通释》,该书虽已散佚,但许多重要条目皆为宋元以来诸家《四书》所引述,影响甚大,至今不绝。这与其《中庸》学之冷遇又成比照。事实上,勉斋《中庸》学确实卓然成家,其所开创的《中庸》学派,以其有守有为的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庸》学的诠释和朱子学的向前发展,其思想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节 美国当代朱子《四书》研究:以贾德讷为中心在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亦须具备全球视野,方能整体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即以儒学研究为例,如何突破“东亚化”,实现“全球化”已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走向。近年来,国内的朱子学和四书学(包括东亚四书学)研究非常活跃,但对英语学界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关注不多。①本文拟对英语学界相关成果加以评述,以为国内朱子四书学研究提供借鉴。美国贾德讷(Daniel K. Gardner)师从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始终坚持对朱熹四书学的翻译、研究,先后出版了《朱熹与〈大学〉:新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反思》、《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朱熹对〈论语〉的解读:经典、注释与经学传统》、《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②贾氏的研究以对朱熹《四书》文献的翻译、注解为基础,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中国经典学的重要问题,如经典与理学、经典与注疏、经典与教化、学以成圣等。这些论题亦为当前中国学界关切所在,故甚有必要对贾氏的研究加以论述。
一 朱熹《四书》与理学
与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常用进路不同,贾氏基于对理学与经典内在共生关系的认识,选择从儒学经典切入展开理学研究。他在《朱熹与大学》序中提出,英语学界尽管对新儒学有了各种研究,但几乎无人关注新儒学和儒家经典的关系。这种不幸忽视鼓励了早在宋代就被新儒家反对派提出的观点——新儒学学说的产生几乎与儒家传统经典无关,更多地来自佛学而非儒学。作者对此予以鲜明反驳,强调本书的核心就是要矫正过去对儒家经典的忽视,确信宋代新儒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深的敬意,并从中汲取灵感。①故贾氏的研究始终关注经学与理学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贾氏认为儒家思想离不开经典。儒者在寻求灵感和指导时求助于被认为包含了儒家思想基本教导的经典文本。读经不仅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义务,更是一种参与古代圣贤对话的方式。四书取代五经原因虽多,最根本的则是对佛教的应对,这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本体论。与五经相比,《四书》更集中关注人性、道德的内在根源、人与宇宙关系问题。贾氏虽亦认同新儒学受到佛教刺激,但其思想的根基却在于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其资源主要来自被重新改造了的儒家经典《四书》而非佛学。故贾氏直接投入于作为新儒学核心资源的朱熹《四书》,从儒家经学史立场来看待新儒学。
他强调从对朱熹《四书》文本的研究中察知新儒学和经典的关联。在所有新儒家中,朱熹与经典联系最紧密,其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的发展是复杂的辩证关系,朱熹走向经典解释正基于其新儒家哲学的核心信念。②他基于自身的本体论假定人皆有能力对经典作出有意义的思考。
之前的学者也相信过去圣贤在儒家经典中传达了真理,但朱熹与他们的差异在于在文本中追寻何种真理。宋代之前的经典学者普遍寻求有限的限定真理,即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境遇,如何给出最有效管理民众的处方;而朱熹则是在寻求一个普遍真理——宇宙中既内在又超越的一个真理。③自此,儒家经典不再是指示性的,而是体现了宇宙中包含一切的普遍之理,这个理将会向任何读者显示。当然,朱熹认为文本中的真理并不易获得,因为没有任何词语能完全表达圣贤的深刻含义。
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阅读》的诠释中,论述了朱熹形上学及经典诠释的几个特质。他指出“我欲仁”章朱注采用了本体论的信仰,使孔子的评论完全明白易懂,把握了《论语》个别篇章与更大传统的关系。朱熹根据孟子的人性论观点来论证本章:一方面经典文本的认同给了这段《论语》更深的共鸣和更连贯的意义,同时加强了《孟子》立场的合法性和意义。最终使得把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变得更有说服力,孟子人性先天本善的观点也显得更自然和更权威。这都说明朱熹的注释起到了联接文本自身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儒家更大传统的中介作用。①他又以“性相近”章为例提出朱熹的《论语》文本和形上学之间关系是动态的:形上学阐发了《论语》的教义,教义使得形上系统富有意义。这种教义与奠基于形上基础的注释的相互交融使它们根本兼容,反过来给形上学一个“儒家”的有效性和意义。
二 朱熹《四书》与经典诠释
贾氏认为儒家经典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典的面貌实际上又由注疏塑造。儒家通过行间注释来表达对圣贤之言的理解和自身哲学思想,经典注释成为追随儒家之道的主要哲学表达模式。②他根据经典诠释方法的差异划分经学史的发展阶段,显示出独特的视角和对经学诠释方法的重视。指岀宋代有三种经典研究方法:考据性(the critical)、经世性(the programmatic)、哲学性(the philosophical)。第一种探究经典文本、注释的著者及其真实可靠性。第二种关注经典中的古代制度、系统或道德价值,讨论其对现实环境的可运用性。第三种是宇宙论解释,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或人道德的内在性。此三种方法乃包容而非排斥关系,他据此对汉宋经学作了发展阶段的区分。第一阶段始于中唐至北宋,考据性方法流行;第二阶段为北宋初期,考据性方法继续流行,经世性方法发展起来;第三阶段是方法多元性时期。前两种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同时逐渐出现哲学性方法,以周敦颐为代表。第四阶段表现为哲学方法的唯一性,《易经》和《四书》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以张载、程氏兄弟为代表。第五阶段是宋代经典解释的成熟和综合期,这一舞台被朱熹主导。③
他又认为,当今儒家经典主要有历史和哲学两种解经方式。一种是通过广泛的文献考察来发现、重构作者试图在文本中表达的意图,另一种是非历史的、哲学的解读方法,试图寻找文本中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内容:即文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作者的《朱熹与〈大学〉》一书采用的就是其一贯的历史学方法,它首要关注的是文本是如何被理解及为何作出这种理解,而不关注是否应当作这种理解——优先关注事实解释而非价值判断。尽管所有的经典解读法都是合法的,但却指向不同目标。历史方法的解读试图至少揭示出中国过去儒家传统的动态发展。其基础是相信儒家文本的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解读者眼里是不一样的,故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思考不同于郑玄等汉代儒者是很正常的。
历史性与哲学性注疏的比较。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中着眼于研究视角和诠释方法,以朱熹、何晏对《论语》的注释比较为例,具体阐明了儒家经典是如何被加以不同诠释的。就诠释视角论,何晏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朱熹则从伦理和哲学的角度。与何晏不同,朱熹直接在注疏中发表看法,引导读者,认为读者不仅应当理解文本的意义,更应明白文本的普遍应用性。①如“礼之本”章,何晏的注释仅仅是重复夫子的话,是描述性的,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相反,朱熹的注释在篇幅上通常比经文长很多。朱熹认为,夫子的评论被弟子组织起来构成《论语》一书,成为一个有深层内在连贯意义和洞见的文本。这一点对朱熹来说几乎是一种信仰。②朱熹认为通过对圣人之言的持续研究、体验,他已经完全获得了这种洞见。这种对文本真理的理解、洞见对所有人也是敞开的,只要他们愿意为此努力投入。他的注释就是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一种帮助,向他们揭示自己有本在文本中已发现的真理。
贾氏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诠释者的角色和目的;如何根据自身思想来重塑《论语》。自我角色定位就是如何理解注释者与文本、传统、读者的关系。在何晏那里,前辈之说具有完全的权威性,在朱熹这里,只有二程等支撑其观点时才有权威性,在经典、权威、读者的三层关系中,他将自己置于整个对话的中心。何晏在诠释中尽量少地“发声”,朱熹则相反,原因在于朱熹的态度是传教灌输式的(proselytizing attitude),带有某种论辩性。这种对《论语》文本深刻的,几乎是宗教义务性的态度清楚解释了朱熹艰苦的注释努力。对朱熹来说,《论语》的价值在于对人具有深刻的转化作用,正是这种对《论语》权威和效果的信仰促使朱熹穷毕生之力注释《四书》。①他的注释尽力使读者相信儒家传统在宋代仍然是有生机和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信仰辩护(as an apologetic)。他认为把《论语》塑造到一个对当代读者有意义的传统中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需要使读者相信孔子的教导和他们的世界是相关联的。朱熹通过对经典的自我反思,自信有能力把握圣人原意,确信他的心与圣人之心已经变为一个。②朱熹确实已经获得了对理的彻底理解,进入了圣贤之境,圣贤之意已极其清楚 地向他显现出来。朱熹和何晏在《论语》中表达了不同的形上系统,决定了他们对圣贤之意、对道的理解的差异。
篇内连贯和文本互涉(intra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references)。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主要探究了行间注的体裁,突出了它在中国知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作用。③自汉代始,行间注便成为主要写作文本形式,该书试图探究以下论题:朱熹为何采用集注形式?如何理解注者和文本的关系?如何协调过去圣贤之言与当代读者的信仰、约定?朱熹的注释如何形成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它如何受到早期注释传统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此后 《论语》的理解?该书通过对何晏《论语集解》与朱熹《论语集注》的翻译、分析,阐明经典文本和集注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作为知识表述的一种工具,行间注不是简单的去文本中发掘灵感和意义,而是同时给予文本意义,极大地构成和重构了对文本的阅读。贾氏从《论语》中挑选了学、仁、 礼、政、道、君子等直接内在关切于儒家核心思想的篇章,以突出朱熹极大改变核心文本意义的方式,显示行间注理解对把握中国传统是如何关键。
贾氏指出,假定文本是一个内在整体是朱熹所有注释重要而鲜明的特质。朱熹认为儒家经典是一个内在综合的整体,每个部分都给整体以意义,正如整体阐明部分一般。这种融合贯通的努力深化了《论语》文本的经典性,特别是强化了四书的核心性,通过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对于愿意倾听者来说,它是开放的,可以进入的。如“博施济众”“十室之邑”“三十而立”等章充分体现了朱熹文本互涉的诠释特征。这种方法给予每种文本合法性,在突出文本内在关联和一体性的同时,还使得彼此更加好懂。著者以《论语》中关于“仁”的9章为例,指出朱熹的评论促使读者依靠整个《论语》及其注释的相关背景去阅读《论语》,这种整体性、一致性是何晏注所没有的。朱熹甚至超越了《论语》文本自身,使夫子的语言纳入更大的儒家哲学视野。著者指出,何晏与朱熹对克己复礼理解的重大差异在于前者认为礼产生了仁,后者则主张仁产生了礼。这种差异在美国学者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和史华慈的争议中同样体现出来,前者的主张近乎何,后者近乎朱。
三 朱熹《四书》与德性教化
通过经典来推行教化是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根本任务,贾氏非常关注此 点。他指出宋代思想发生了由外王至内圣的“内转”,在此转变过程中,朱熹的最大贡献是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对 《大学》的理解发展出来。①朱熹对《四书》的重视超过五经是因为他认为《四书》体现了道的本质。在《四书》中,《大学》应最先学习,它比任何一部儒家经典都更简洁地表达了儒学之道的广阔目标:个人修身和社会治理。朱熹对《大学》个人式的、宗教性的解读(this sort of personal, religious approach to the Ta - bsueb)导致对文本全新的理解,与传统上对经典理 解相比,至少有三方面重要突破:首先,汉唐学者主要把《大学》理解成仅为统治者使用的政治手册,朱熹将之看作所有人自我修养和社会治理的指导,扩大了《大学》的读者范围。其次,朱熹发现了《大学》里面的一个 本体论假设和自我修养过程后面的目标——明明德,朱熹认为明德不是向外展现德性或德性行为,而是内在道德心或每个人降生之初的天赋之性,它可能受到物欲或人欲的污染。贾氏认为其实朱熹的明德是包含了心性的一个整体。第三,朱熹认为《大学》规定了实现性的正确途径一格物,它被视为整个自我修养过程的第一步和基础。朱熹在格物补传中对此作了雄辩阐发,特别讨论了觉悟问题,他把格物作为儒家矫正佛教静坐的方法,它可以导向自我实现和升悟境界,同时又是自我与社会连接的中心。
学以至圣。贾氏所译七卷《朱子语类》的正标题是《学以成圣》,意在表明朱熹的中心关切是如何学以至圣,即道德上的充分实现。他的形而上学综合代表了儒家哲学的新发展,试图给人的道德完善这一儒家传统教学目标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对朱熹来说,人之天赋性同气异,气的量质将决定人性是呈现还是继续被遮蔽。朱熹对此给予了最多的哲学关注,给弟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系统、渐进的自我完善工夫,工夫程序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格物。格物是改善自我和本原道德之性的手段,是自我觉醒、回归真我的过程。
基于此,贾氏《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通过对《朱 子语类》中有关学的篇目译注来显示如何经由学习达到圣人境界。该书据清代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选择“为学”七卷加以翻译,详尽分析了朱子为学生设计的学习计划。诸如“学”为何意?何者为核心课程?如何学习文本?读者与文本关系如何?他认为与北宋学者相比,儒家发生了由确认一个有道德的人到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转变。①由传统的如何发现贤人转变为如何培养贤人,朱熹倡导《四书》作为核心课程,吸引学者更多地走向内转反思的精神生活,而非外在的政治参与。贾氏确定《论语》的第一主题是“学”,在比较何晏、朱熹注释差异时指出,何晏的“学”仅仅是对合适文本的诵习熟读,朱熹的“学”则带有明显的道德目的。②
贾氏在《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中提出,朱熹尽力于《四书》就是要解释孟子提出的两个哲学问题:如人性为善,恶从何来?如人性为善但如何实现之?朱熹对人性内在潜在之善与实际行为之善存在的鸿沟加以精致的哲学化解释,其哲学系统就是将自我修养过程视为中心论题。要实现这种完善,意志和努力是根本的,格物又是工夫第一步。学习体验《四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服务于修身,通过修身使道德呈现于各种相互关联中,仁就是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Goodness' is to be good in one's relations with others .①仁的字形亦表明它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中获得。苦行者数十年坐在叙利亚沙漠里的柱顶来消除心中恶魔,以便在上帝眼里变好,这在儒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儒家认为政府具有一种最高权威,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来推进人民的道德发展。好的政府应当是有德行的,它的管理依赖于道德力量、礼仪实践而不是法律,这是儒家洞见的政治基石。《四书》支持的政府形式是一种仁慈的家长主义,统治者对民众有着如父亲对子女般真诚深厚的关心。在《四书》看来,理想的政府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道德命令,好的政府使人民变好。②这使得儒家的政治教义与其他大多数的政治哲学不同。但在《四书》中存在一个教义的循环,即政府好人民才会变好,但只有好人同意为政府服务,好的政府才有可能。故中国统治者依赖于科举来发现这样的人,这又依赖于对《四书》的学习。
四 朱熹《四书》与经典翻译
贾氏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翻译基础上,对《四书》相应术语的运 用体现出其本人的思考方向。以“经典” 一词为例,贾氏在论及儒家五经、十三经、《四书》时,采用了 Canon 一词,而在表达一般意义上的经典时,则采用Classico这两个词最根本的区别是Canon指“A collection or list of sacred books accepted as genuin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该词来源于基督教,常指《旧约》、《新约》,带有明显宗教意味。但是否能仅据贾氏使用该词来断定其对朱熹《四书》研究是从宗教学研究角度出发呢?贾氏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其一贯的研究方法是在《朱熹与〈大学〉》中已指出的客观、平实的历史研究法,以如实把握朱熹的经典思想。他的朱熹研究并无任何宗教意味,尽管他曾指出朱熹对《四书》研究的执著已带有某种宗教情怀,但只是意在表明朱熹的研究态度。作者使用Canon意在表明儒家思想系统中具有《圣经》般地位的经典已由五经转换为《四书》,以此突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经朱熹诠释后,已成为真正的Canon,影响统治了中国后期的知识史,非一般Classic可比。它所指的是《四书》的经典地位而非表明作者对朱熹研究的宗教态度,并不能以贾氏之书来证明西方朱子学研究的宗教性趋势。①
诠释的主观差异性与文本的客观同一性。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 读》一书以比照方式突出了何晏《论语集解》历史诠释与朱熹《论语集注》哲学诠释两种方法的差异,就《论语》何、朱不同注释直接给出不同翻译,区分了不同学者视域中的经文,达到了彰显朱子新经学与何晏经学不同的目的。
如:时习之,何:以时诵习之。recite it in due time;朱:时时习。re-hearse it constantlyo②与其易也的“易”。何:和易。serene.朱:易,治也。meticulous.③又如“有耻且格”的“格”,何:格,正也。Set themselves right.朱:格,至也。……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Arrive at good.④朱熹对,,格”的第一解为“至于善”,第二解则同于何晏。他曾明确表示,如两解并存,以第一解为优。
贾氏的翻译存在变易。19世纪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奠定了西方中国经典翻译的典范,他对《四书》的翻译亦以朱熹《四书》为底本,将贾氏对《大学》主要范畴的翻译和其译文相对照,可见出贾氏的特点。下文J指James Legge, G1指贾氏1986年版《朱熹与〈大学〉》译文;G2指其2007年版《四书:后期儒家基本教义》译文。
明明德:J : 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
G1 : keeping one's inborn luminous virtue unobscured
G2 : letting one's inborn luminous virtue shine forth 格物 J: investigation of thingso
G1 : apprehending the principle in things
G2 :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就字面意义对称而言,“明明德”两个“明”字只是词性不同,意义并无多少差别。贾氏的翻译过于曲折,不如理雅各精准。贾氏2007年译文较1986年在语义上更具积极性、主动性,但仍不够简洁。早期贾氏对“格物”的翻译,意译为“穷究事物之理”,亦不够恰当,若 此,则如何翻译“穷理”?故他在2007年重新回归理雅各的翻译。此外贾氏对仁、新民、中庸等的翻译与理雅各亦有不同,然其高下则各有千秋。
贾氏译文亦有可商处,如他对何晏、朱熹的“克己”有不同翻译,何:to restrain the self;朱:to subdue the selfo① 何晏引马融说把克己解为约束自身,朱熹则解为战胜身之私欲。其语义有两处差别:“克”是约束还是征服? “己”是身体还是作为身体中不好的部分(私欲)?贾氏注意到前者之别,但却将两个意义不同的“己”都译为“self”,显然未达到区别的效果(就笔者寡见所及,英译本少有注意此点者)。即便在朱熹本人的诠释中,此克己之己与本章下句“为仁由己”之“己”亦是意义有别的。
贾氏认为朱熹诠释具有语篇连贯和互文性特点,故对其《四书》的翻译诠释亦采取了整体比照和局部探微相融合的方式。他对具体文本的翻译,总是结合其他相应文本来阐明之。在翻译每条《朱子语类》正文后,适当以小号字体加以阐发,并另外加以注释,基本上引朱解朱。如第七卷小学第一条,即引《大学章句序》解释古人小学和大学的问题。对某些重要核心术语如理气等,贾氏不遗余力的旁征博引,此引注法实得朱熹精髓。既然何晏、朱熹对《论语》有着不同注释,那么《论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贾氏认为,《论语》的真正意义就是读者在文本中发现的意义。《论语》滋哺了保留它为神圣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恒久的重新诠释和重新振作的自我认同中反过来滋哺了对《论语》的阅读与理解。故对注释的学习之于经典文本实际意义的理解珍贵无比。
综合来看,贾氏的朱熹《四书》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比较的研究视野。他把握住朱熹《四书》作为晚近儒学的基本教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和谐整体。并利用《四书章句》之外的材料展开比照性研究,明确了各资料之间的主次先后关系,指出《语类》虽然极具参考价值,但还是应最先参考《四书章句》。通过何晏、朱熹《论语》诠释的具体比较,发现中国经典诠释存在历史与哲学两种模式。二是内在问题意识。著者选择由经典诠释入手来研究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对西方忽视中国经典研究的补充。他注意到注释是中国思想家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故在《四书:后期儒家基本教义》中采用集注的研究形式向英语学界阐释自宋以来理解《四书》的典型方式。其次,著者对中国经典的学习载体——朱子《四书》;表达形式——行间注体裁;诠释方式——魏晋的历史性与宋明的哲学性诠释;学习目的——学以成圣等重要问题都有细致阐述。这些论述对西方目前仍缺乏的中国经典思想研究有很强的补白意义。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历史后半期( 1200—1900年)中国人如何研究《四书》文本并吸收其中的价值观,这在西方极少有研究。另一方面,著者的研究涉及理学经典化、经典诠释义理化、经典宗旨伦理化等重要经学思想论题,对当前日益活跃的经学思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如贾氏认为,朱熹《四书》诠释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理、气、心、性构成的一套形上语言和儒家正统结合起来,提供了更加人类中心主 义的关切。三是采用了以传统经典注释方式为主,辅之以西方论文的形式,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其著作由长篇前言+翻译+注释+结语的结构构成,翻译注释皆极详尽,如对《大学》全书的翻译包括了《大学章句序》,指出“复其性”来自李翱。对已有注释加以批驳,如批评理雅各将“下民”解释为“inferior people”不妥,应为“ the people below ”not“the inferior people”.①当然,贾氏的从思想史展开研究,对朱熹《四书》诸多内在哲学问题如道统、理气、心性等并未给予深入阐发,此是其限制所在。
中国哲学以重直觉体悟、轻逻辑论证为特点,哲学家对哲学的看法常以口语即兴的形式表达,缺乏对范畴的确切界定。宋代理学在继承传统儒学固有特色的同时,亦体现出对范畴之学的关切,出现了专门诠释理学范畴的“字义”体。探究这一“字义”体的演变历程及特征,有助于认识理学的范畴之学和四书学,增进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朱子对四书的精密注释实为“字义”学之先导,程端蒙《性理字训》发其端,陈淳《北溪字义》显其成,三传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扩其域。私淑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五传朱公迁《四书通旨》则皆以“字义”为纲,类聚经书正文,分别形成“字义”+注疏、“字义”+“经疑”的综合体。朱子门人后学创造出来的“字义”体,构成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样式,具有类聚范畴、专注义理、定位蒙学、理学指南的特质。尽管其“摆落章句”“类聚字义”之做法未见得为朱子所认可,然其直指范畴的诠释方式,实为中国哲学范畴之学、四书学的发展,显示出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之继承与创新。
一 开端之作:《性理字训》
理学“字义”学与朱子密不可分。朱子生平好章句学,重范畴辨析,凝聚其毕生心血的《四书章句》对诸多概念有着精密界定,体现出“浑然犹经”的特色,达到了“字字称等”的地步。为此,朱子门人后学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体裁对之作了多样阐释,发端于程端蒙、大成于陈淳、变异于真德秀的“字义”体,则构成阐释朱子《四书》的一种新样式。
朱子素重童蒙教育,撰有《童蒙须知》等著作。“字义”即弟子承此思想而作,意在教化童蒙,为童蒙日后德性养成打下基础。程端蒙《性理字训》言:“凡此字训,搜辑旧闻。嗟尔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义。……圣贤可致。”①可见该书乃是初学小子掌握理学名义,成就圣贤的启蒙之作。朱子又称其为《小学字训》。该书仅380字,以四字句形式对理学30个主要范畴作了精炼概括,简明扼要,易于记诵是其最大特点。如“仁义礼智”仅用三句短语训释,“诚、信、忠、恕”仅以四字训释,简略至极。朱子对该书有两种看法:既高度称许其训释之功堪比古代第一部词典《尔雅》,认为该书“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②。又对其简明有余、精确不足有所批评。他曾与黄榦论及此点:“如仁只说得偏言之仁,不曾说得包四者之仁。”③认为该书“无所偏倚谓之中”仅阐发了在中义,而无时中义。“仁”仅阐发了偏言意义之仁,而未顾及专言之仁的统领义。此非著者理解力不足,而是为定位训蒙所累。
尽管该书有粗疏偏颇之不足,然作为“字义体”的首创,其先导之功仍具不可忽视之意义。就选词论,该书30个范畴几为后出同类著述全部取用,构成“字义”体的核心范畴。就内容论,所选范畴侧重心性、道德、工夫,缺乏天道本体、治道外王,此亦与其定位童蒙有关。此外,该书漏收“意”这一心性论重要范畴。其范畴训释多见于朱子《四书》,如以“真实无妄”释诚,“主一无适”释敬等。该书亦有其创新:一是补充朱子所未明言者。如把“智”训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谓”,突出智之“别”义。二是编排颇具匠心,把“命”置于所有范畴之首,居于“性”之前,《北溪字义》亦袭此。
比较《性理字训》与《北溪字义》范畴及编排,可谓“大旨相同”。《字训》范畴大致分三组,命、性、心、情、才、志前六个为心性组,《北溪字义》与其序一致;“仁义”至“孝悌”诸范畴为德性工夫组。《字义》则有不同:一是将具内在联系的两个(或更多)分说的范畴合并为一个范畴。二是调整范畴次序。如《字训》“信”与“诚”相邻,《字义》则置“信”于五常,同时又在“忠信”中予以讨论,而将“诚”与“敬”相邻。三是范畴不相应增多。《字义》另列“恭敬”,取消《字训》之“孝”“悌”“一”。《字训》天理人欲等四对范畴为成德境界组。《字义》则自“道”始为下卷,论本体、成德、鬼神、异端。并增加了《字训》所无的皇极、礼乐、经权、鬼神、异端。盖在陈淳看来,这些皆是圣贤成德境界所应有之效用,乃内圣必备之外王。
二书之差别主要见诸义理阐发之深浅。《字训》纯为初学者设,“颇为浅陋”,《北溪字义》的出现使得《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已无著录价值,故仅将之归为存目,甚至因该书水平不高而怀疑该书为村塾先生所作,这是缺乏历史眼光而有失公平的。①
二 典范之作:《北溪字义》
《北溪字义》以其“抉择精确、贯串浃洽”(陈宓序语),将“字义”从童蒙之学提升至“经学之指南、性理之提纲”(顾仲序语)的高度,树立了“字义体”的典范,标志着诠释《四书》新样式的形成。学界诸贤对该书的研究已有诸多重要成果,今拟就若干问题再加讨论。
题名异议。关于该书题名,两位前辈学者有不同看法。邱汉生认为该书应命名《四书性理字义》方全面确切,他说:“从书的内容考察,当以名《四书性理字义》为较确切、周匝。盖《四书》言其范围,‘性理’标其性质,‘字义’指其体例。”②陈荣捷则主张应名《北溪字义》或《性理字义》,不赞同《四书字义》之名,理由是四书不足以概括其中三个范畴:太极、释、道。邱氏已注意及此,认为既然《四书》能概括该书绝大部分条目范围,就足以作为书名,个别范畴无法概括并无关系。他特别以“羽翼《四书集注》的《四书性理字义》”为题,提出《北溪字义》是“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等二十五个范畴,逐条加以疏释论述的书。……是理解朱熹《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①。愚以为,“字义”所关注的朱子“四书”,是以《四书集注》为中心,辅之以朱子有关四书论述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太极”等个别范畴实亦纳诸其讨论范围内。以四书命名,并无不妥,可足显其醒目之效。
该书实为阐释《四书集注》的新样式。古人对此早有高论。施元勋序据《近思录》为《四书》阶梯之说,提出《北溪字义》为《四书章句集注》的“阶梯”说。“亦愿今之读《章句集注》者,以是为阶梯尔。”②宋李昴英序认为二书是源流关系,学者当“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邱汉生进而认为该书是“解释《四书集注》的第一部书”。③该书是否是第一部并不好说。朱门弟子对朱子思想的体会皆不离对《四书集注》的研习,黄榦等对该书皆有阐发之作,虽未完整留存,但多少保留于注疏中。再则,该书体例并非解释《集注》之书。历来目录著作,皆不置其于经部,而视为童蒙类置于小学类或史部,《四库》即置其于史部。故就形式论,该书非阐释《集注》之作;就实质论,可视为阐释《集注》范畴的专题之作。
该书范畴之选取及其编排,成为近来学界的关注点。张加才提出可据该书卷上、卷下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部分,进而再分为心性论、道德论,理本论、教化论、批判异端论五部分。④邓庆平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上卷所选之‘字’属于性情论、道德修养论的概念,下卷为本体论、境界论和批判异端。”并在范畴归属上,将张加才教化论的“义利”划归“批判异端”。⑤
二位学者力求找出二十六个范畴逻辑划分的努力,总令人感觉不踏实。比如从何种意义上把“皇极”视为本体论范畴?“义利”如何属于批判异端而非成德之目?窃以为,对其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仅能大概而论,不可过分较真。首先,该书非陈淳有意识的构思之作,乃弟子王隽所录讲学结果。其卷次、字次编排是否有精心构思,实可存疑。其次,该书毕竟兼有启蒙性质,以阐释朱子《四书》范畴为中心,追求范畴之精当解释,至于范畴之联系,非其考虑重心所在。最后,即便有内在“逻辑”,恐亦非直线式,非此即彼的逻辑,古人讲求融合、通透、灵活、贯通,逻辑以“两即”为特色①。该书正体现了“玲珑透彻”的相即性。陈淳指出,道理是贯通循环的,当对道理的领悟进入圆通熟透之境界,道理之表述则横竖皆可,不拘于一。“此道理循环无端,若见得熟,则大用小用皆宜,横说竖说皆通。”②
该书开篇即告知理解此书之法,言“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渐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单看本字须亲切,合观多字须玲珑透彻。玲珑具清越、明彻、精巧、灵活诸义,它提醒读者应注意诸范畴间同中有异、分中有合、相互渗透的特点,做到明而不乱,灵而不滞。元儒陈栎对该书的把握亦是玲珑精透,称《字义》一书玲珑精透。③此一特色与陈淳范畴诠释原则亦相应,他在阐发“道”时提出一重要观点,即“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方可”④。他以实例为据,指出同一“道”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有“就造化根原上论”和“就人事上论”之别。可见,若过分追求该书范畴间严密的逻辑体系,恐不合古人立言宗旨。
关于诠释形式。《北溪字义》成为“字义体”典范,不是因其释字多,篇幅长,而是因其“简而该,切而当”的阐释特色,为“宋代理学最简明之叙说分释”⑤。全书仅收26个范畴,为同类著作最少,然看似范畴少,实则如细致析分,恐亦近乎百个,因其条目最多也。
该书诠释最大特色在于注重范畴的界分与脉络。陈淳认为“字义”间具有某种类似脉络的连结关系,对某一“字义”的精确“界分”,须结合其脉络进行,置“界分”于“脉络”中。一方面,精于“界分”,突出比较,构成该书特出之处。该书对范畴异同辨析高度重视,常将之置于正面下定义之前。如诚,首言“诚字与忠信字极相近,须有分别”①。鉴于字义的复杂丰富性,陈淳在“五常”的阐释中提出“竖观”“横观”“错综观”“过接处观”等多角度的字义审查方法。所谓“竖观”,即五常各自有其对应之物件和含义,略似于分而论之,强调每个范畴的独立性;所谓“横观”,指用综合的眼光考察范畴间联系,近乎合而观之,突出范畴的有机整体性。所谓“错综观”,凸显的是范畴既具有内在的独立自主性,又与其他范畴存在相互错综、彼此包含、内在融贯的一体关系,其实即“横竖并观”。所谓“过接处观”,亦是就范畴间联系而论,强调在某一范畴中已内在“酝酿”着相关范畴,范畴之间是相生互具的。
析一为二的“二义”法。陈淳大量运用“界分为二”法,最典型的是直接将范畴两种含义点明,如“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次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将某一范畴切分为二,多是成对范畴,如理气、心事、心理、内外、天人、自然用力等,具体可参其对诚、忠恕、仁等字义的解释。还有“就某方面而论”者,如命可分为“就人品类论”“就造化上论”两类。较常用的区别术语有“正面一边”“言上事上”“浑沦分别”等。与此同时,陈淳亦再三提醒应注意范畴间的脉络关联,不可将之视为“判然二物。”如“忠信非判然二物”。“非二”要求从范畴间一体关系出发,强调“即一”。他特别批评韩愈对仁义、道德理解之误在于判二者为二物,“是又把道德、仁义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②。
陈淳对“字义”脉络与界分辩证关系有深刻把握,提出“浑然中有界分。”如不加以细致分析,则无法看清各字义的独特意义,如仅顾及个别字义而不将之置于更大范畴之网,则无法把握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盖范畴之间“元自有脉络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③最合理的方式是将“界分”置于范畴之网,既能把握范畴之间的联系,体会其相似性,又能加以精确区分,掌握各范畴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引起字义的乱用,即“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①。陈淳还强调了处理范畴关系的灵活性,提出“不可泥着”。
三 扩充之作: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
(一)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
元程若庸曾问学饶鲁,为朱子三传,他对《性理字训》加以增补,将范畴扩充至183个,此后明代朱升又据袁甫说增加“善”字,为184个。该书特色是大大扩充收字范围,数量为同类之冠,且将所收字明确分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大门类,在每门末加以总结。《性理字训》所收范畴主要见于该书情性、学力、善恶三门,故其他三门几全为增补。与前此二家置“命”于首不同,它以“太极”居首,同于《近思录》之首列“道体”。程氏认为,“太极”作为造化本原的字义,具有广大精微的特点,对初学而言具有难度。将其列之于首,希望学者通其名义,知学之标的所在,以之为终生求学之目标。该书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的安排,展现出由天道本原,经由人之心性、工夫、德性、境界,落实于治理教化的过程,全面周到。其新增范畴多取自《四书》,有些已为《近思录》所取,可证该书确是参考了《近思录》。此外,不少范畴如“理一、分殊”等直接取自理学话头,显示出字义体阐释理学四书的宗旨。
该书仍停留蒙学水平。各范畴既孤立无联系,又多交叉重复,甚者同一“字”作为两个范畴出现,如造化门分列两个“天”,分别作为自然形体意义上和义理意义上的天。此并非偶然,乃故意为之。该书对“道”的处理亦如此。一是造化门生成万物无声无臭的形而上之道,二是情性门作为人伦事物当然之理的共由之道,即伦道。此外,该书尚另设有天道、人道、达道、小道四个范畴,前三者皆属于“情性”门,“小道”则属“善恶”门。照《北溪字义》的处理,应属于同一字的不同义项,作为两个“字”处理,显然不合适。无怪乎四库讥其“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该书虽仍拘泥于四言童蒙式,但影响颇大,成为理学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本,元朱升将之与《名物蒙求》等并列为小学“四书”。后世多以该书取代《性理字训》。元程敏政认为该书体现了朱子童蒙教育思想,要求童蒙八岁入学前,每日读该书三五段,视之为替代世俗《千字文》等蒙学教材的最佳读本。“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日读《字训》纲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①此外,元史伯璿《管窥外篇》提出该书有白本、注本之分,其流传、异同颇值留意。
(二)陈普《字义》
陈普,字尚德,号石堂,宁德人,《续修四库全书》收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据《字义后序》可知,陈氏学于浙江韩翼辅,韩氏为辅广之徒,故陈普当为朱子三传。《遗集》卷九所收《字义》一书,是陈普与弟子讲说讨论的结集,选取平日讲说中意味深厚亲切、简洁明白,可成字义者,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布局,共收字义153个,因今本残缺,实存138个,全文约11000字,“多于程正思而少于陈安卿。”陈普对本书颇为自信,认为乃入道之门,可助学者登堂入室。其门人余沙认为,该书较之程、陈之作,不仅篇幅上详略得中,而且在确立字义名目、辨析字义含义上更显精密。②
陈普认为字义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圣贤已逝,道存文中,文由字成,故字义之是否明晰,直接影响对圣人之道是领悟还是背离,继而影响为学效用是专精贯通还是鲁莽灭裂。对字义之慎思明辨,乃笃行工夫之前提,不可忽视。在该书自序中,他反复强调性命道德等字义对六经四书具有纲领、灵魂的意义,学习作为六经四书之精华的字义,是进入经书要领所在,决定了能否明乎大道,领悟圣贤之心。对于明道成圣而言,具有门户和唤醒的功能,是必由之径。此显示出陈普对字义学有着自觉认同和高度评价。
明于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字之义,则六经四书之全体可得而言矣。世之知书而或不明于道,不得于圣贤之心者,未明于此等字义故也。明于此等字义,则千门万户以渐开辟,当如寐之得醒矣。③
陈普清醒认识到字义的复杂性,提出“字一而义不同”说。字有其最初本义,亦有其后来之引申义,本义与引申义又有着内在联系。以“道”为例,本义共由之路与引申义之间,距离看似很远,其实仍有迹可循。“一字一义,有一字而数义者……其义之相去若甚远而究其终,皆同出也。”①他很关注“字”的语境义,如指出“安”在不同语境中具不同含义,“恭而安”、安行之安乃是“不思不勉而自无不合道之安,圣人之事也。”安土、静而后能安之安乃是“乐天知命之安,圣贤之所同”。安其身、利用安身,乃“不愧不怍,无过无罪之安”。并指出“静而后能安”,据朱子“无所择于地”解当与“安土之安”同义,学者理解多误。鉴于字义“不可以一二名”的特点,该书尤留意字义的细微区别,此为该书特色之一。
该书特色之二是设立了“人”“物”“止”“一”等某些较为新颖的范畴,如专立“人”范畴,指出人得天地生物之心而为心,进而从三才之道的立场推出人由此为天地之心,居三才之中。正因“人”内在的具备仁,故与仁同音,孟子“仁者人也”说即表明作为恻隐之心的仁充溢表现于人之体内,以突出人、仁的一体性。如“物”范畴,认为其意为“实也。天地间万物万事皆道之实体也。理之所有而不可无者也。”以“实”解“物”,比较罕见。
该书特色之三在于以“公私”“理”“诚”作为核心范畴贯穿全书。如“诚”的诠释,其基本义为真实,“诚,真实也。”与《北溪字义》强调“无妄”不同,陈普突出了“不杂”,指出诚“全体皆天道”,是天道的呈现,“不杂”表现在两方面:不杂他道异端,不杂外物。“全体皆天道而无他道外物之杂也。杂他道外物则为伪妄而害其体。”②如掺杂他道外物,则是虚伪胡乱,将伤害天道诚体,必须消除之方为真实。陈氏立论当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鉴于现实生活中学者用功不纯之学弊而发,二是针对学者惑于异端之学而发,强调诚者天道,天道乃是最真实无虚纯粹不杂者,非天道者则为虚伪妄乱,背离了诚。明白诚的天道意义,则可以辟除异端而不为所惑,这一思想与程子“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说有关。在“一”的阐释中,他继续强调“诚”的纯杂之辨,“所谓一以贯之之一,诚者之事也。去其杂以纯其体,防其间断而常久其功,此则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诚之者之事”①。一贯之一表达的是诚者始终保持于纯粹无杂之境界,精一、克一、主一乃是强调当如何去其杂质以纯其诚体,并持之以恒的诚之工夫。他称赞蔡沉“不杂之谓一、不息之谓一”解“最尽”。不杂、不息正是从纯一不杂的角度解诚。此当本于《中庸》“为物不二”、程子“一心之谓诚”、朱子“一于善”说。此外,陈普在对信、虚、实、名、实等范畴的诠释皆以“诚”相释,可见“诚”之枢纽地位。
勇于批判理学前辈之说是该书另一特色。陈普对作为理学“字义”源头的朱子《四书集注》即有不满。认为朱子对《告子》上篇的注释在本意与文义的处理上存在问题,一是本意不对而文义对,如“生之谓性”注。二是本意对而文义不安。如注中所引程子“才禀于气”说。并指出《集注》“朋来之乐”取程子说,将之与“不知不愠”合而为一,仅仅看到二者在同一章内皆阐发“乐”这一范畴,而没有察觉“字一而义不同”,“乐”具有差异性与层次性,不愠为深层次的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乃是较低些的乐。
文公以朋来之乐与不知不愠用程子说,合为一于注之末。盖只缘章内一字为注。其实,朋来之乐犹浅,不知不愠始深。不知不愠即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亦渐有意耳。②
陈普把另一批判矛头指向《北溪字义》,认为它同样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某些字义的阐释不准确。如关于“极”字后段采用己说处多有不妥。二是收字范围太过狭窄,影响了广度。如“三才”丝毫未提及。据此看来,陈普似乎有意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陈淳。“北溪陈安卿《字义》用文公之说已善,而后段说‘极’字多未当,盖亦未深明也。至于‘三才’则未闻有一语及之者。”③
总之,陈普《字义》晚于《北溪字义》,体现了“字义”学的某些发展。在范畴选择上,设立了不少有特色的新范畴。同时对某些核心范畴如诚、理、太极等的诠释颇见特色,多少体现了字义学的发展。虽总体上无法与《北溪字义》之严密性、精确性、学术性相提并论,但多少摆脱了“浅陋粗糙”的蒙学性,可谓介于蒙学与学术性著作之间。
四 “字义”之变异:《西山读书记》与《四书通旨》
《北溪字义》奠定了“字义”体之典范样式。继此而作者,则将“字义”与其他体裁相结合,形成了“字义”的变异体。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朱公迁《四书通旨》即为此类。二书共同特点是:以若干范畴(“字”)为纲,以四书材料为目来组织全书,此以数十范畴组织四书之形式,可谓类聚。此类聚体现了范畴优先的立场,具有“字义”体特征,类聚之范畴又多源于《四书》,可视为诠释《四书》之作。二书差别在于:《读书记》采用“字义”、《四书》原文(亦有非《四书》者)、注疏的“三合一”形式,为“字义”+注疏的综合;《通旨》则采用“字义”、《四书》原文、辨析的形式,为“字义”+经疑的综合。
(一)《读书记》的“字义注疏体”
此一体裁以传统注疏为主体,除首列一范畴统领相应材料外,其余则纯为注疏形式。先列含所列范畴的四书(或五经)相关原文(或节选),再大量引用程、朱学派之说,间或在按语中表达个人见解。此字义+注疏的综合式,字义起统领作用,经典文本被拆解、打乱、截取,服从于范畴的需要。注疏则摒除了文字音韵训诂、纯任义理,体现了义理解经的特征。所引各家说颇为繁复,不乏相互对立者,目的是为了提供丰富、多样的解说,予读者以思考、抉择的空间。但这种材料的丰富、复杂却让初学者易陷于其中而难以得其要领。故该书并非为初学之教材。此外,该书“理学经典化”意识强烈,常将濂溪、二程、张载等重要论说作为与经文同等的正文形式直接列出,如“性即理也”,《西铭》等,以示理学家论述具有与元典同等之地位。
西山创造出此种字义加注疏的综合体,欲在吸收二者之长而避其短。“字义”体的优长是简明扼要,给范畴以教科书、字典般的解说,缺点是不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想象、理解、选择的空间,易受编纂者思想的限制。又由于它摆脱了训诂、文本,实质上摆脱了字义的历史、思想、文化语境,易给学者枯燥乏味、悬空脱节的感觉。故“字义”只是理解程朱《四书》的阶梯,并不能代替对《四书》和程朱著作的研读。西山在“字义”基础上辅以原典、注释,用意即在于落实陈淳“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理念,避免纯粹字义体的局限。反之,注疏体以材料丰富、解释详尽著称,然其繁琐之弊亦不可免。将二者结合之,则能收取长补短之效。
朱子对类聚言仁颇有疑虑,西山对“字义”亦抱同感。故《读书记》“仁”卷之末特意引朱子、南轩关于类聚言仁的讨论,南轩秉程子类聚观仁的想法,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则担心此种做法会形成贪图捷径的心理,产生口耳之学的弊病,加剧学界盛行的“厌烦就简、避迂求捷”的学风,要求南轩以序的形式将此忧虑告诫之心布告天下,或将二人关于讨论此事的往返书信作为书的附录。南轩接受了朱子的看法,“悉载其语于卷首。”西山指出,朱、张二先生为学者考虑深远周到,今《读书记》以字义为纲领,辑合相关文本,恐亦有前贤所虑之病,故载其说于此自我警示。“二先生之为学者虑也至矣。今类辑此编,亦恐有如二先生所虑者,故书之篇末以自警。”①
《读书记》与《北溪字义》皆为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栎曾加以比较论述。他说:
《读书记》一书既博且精,凡诸经、诸子、诸史、诸儒之书之所当读当讲者,皆在焉,乃有载籍以来,奇伟未尝有之书也。……《读书记》尤博大精微,可以该彼二书,而彼二书不能该此一书也。②
陈栎对陈淳有很高评价,赞他为“朱门第一人”,赞《字义》“玲珑精透”、兼具简明通俗、高妙精要、贯通上下的双重性。但他对《读书记》评价更高,认为该书广博精深,完全可以包括《增广性理字训》、《北溪字义》,实为自古以来罕有的“奇特伟大”之书,为传圣贤之道的不朽之作。就广博和深厚论,《读书记》当优于《北溪字义》。
(二)《四书通旨》的“字义经疑体”
《四书通旨》与《读书记》所异者在于该书纯以98个字义类聚四书原文而不带任何注释,仅在所类聚文本后,对文中范畴之义略加异同辨析,近乎元代科场流行的“经疑”体,可谓“字义”与“经疑”的结合。其最大特点是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字义、义项、含义、文本的四级含摄方式,以“凡……皆此类”“凡几见”等术语把四书文本重新归为98类,实现了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具体而言,每门字义分为若干不同义项,采用“皆是此类”“与此类同”等以义归类的方式将文本安顿在各具体义项下,以此区别范畴之同与具体义项之异。同一义项下又析出若干含义,聚合若干文本,著者对各文本含义的细微差别作简要辨析。通过这种四层分析含摄的方式,最终落实到具体文本,达到通《四书》之旨的目的。《四库总目提要》对其特点有简要概括:“是编之例,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①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较,该书最大程度实现了范畴与《四书》文本的一体化,全部范畴皆来自四书文本,它书所收太极、皇极、天理等因在《四书》外,皆未被收入。《通旨》对范畴与文本关系的处理尚另有一特点,即某一具体文本中虽无某“字”,却可从思想上将其归入该“字”下,显示出思想判定优先的立场。如“上天之载”一条并无“敬”字,却列为“敬”范畴之“持敬之功该动静贯始终兼入德成德”义项下。②
元代科考采用“经疑”问答形式考查学子对朱子四书的理解,着重文本的异同比较,疑似辨析,融会贯通。此一出题特色非常吻合“字义”体。《通旨》虽非科考经疑著作,然对《四书》异同的疏通辨析,带有鲜明的“经疑”色彩,辨析之语如轻重、要领、对反、表里、发明、统言专言、兼言泛言、凡几、偏全等为“经疑”所常用。
《读书记》、《通旨》非标准之“字义”体,除综合性外,二书“字义”之选取并非以纯粹范畴为主,而注重经书的类聚与工夫、事项的大致分类,《读书记》以五经四书之名分列字义,设立《大学》、《广大学》、《易指要》、《书指要》等“字义”,《通旨》则以人物列为字义,设立孔子、子思、孟子等,约有40门“字义”纯为事类,故被讥为“体近类书,无所发明”。较蒙学类“字义”之粗陋,二书略有“微嫌其繁”,不够简洁切要之弊。此外,二书皆不对任何范畴作具体解释,而依次罗列它在各文本中的具体意义,《读书记》尚列出各家注释阐发,《通旨》则特重异同辨析,这是此类著作异于纯“字义”类的又一特色。在注释宗旨上,二书亦不以童蒙教化或编撰简要之教材为宗旨,而是以提供阅读思考之文本,锻炼读者思辨能力为追求。故《西山记》常采用朱子、南轩不同说法,以“读者详之”的案语引导读者加以辨别。
上述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自一传至五传的六部“字义”著作,形成了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模式:“字义体”,是朱子学者对中国范畴之学的贡献,体现出朱子学者的传承与创新。此类著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首先,皆“摆落章句、独崇义理”,放弃了对经典文本的事实性考证,直接以简洁明了的“字义”形式传达对程朱理学的准确理解。无论是大到著述理念,小到具体字义,其论述视域皆不离程朱思想,理气、心性、工夫居核心地位。其次,字义的选取基本源于朱子《四书》,又落实于此书,这是字义体的又一基本特征。朱子四书为朱子一生心血所萃,门人后学以不同形式对之阐发,“字义体”即是门人后学创造出的新形式,它对推动朱子《四书集注》成为理学最重要的经典,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又次,在“字义”阐释形式上,朱子门人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的著述形态,体现为从理学蒙书、理学辞典至理学精华的三次转变。其定位亦发生了蒙学教材、字义模板到四书参考的变化。最后,在“字义”的具体诠释上,门人后学尽管皆以忠实阐发程朱思想为追求,但他们并不忌讳对程朱及前辈的不同看法,而是大胆提出批评和异议,体现出勇于创新的朱子学精神。
“字义体”作为对理学四书的专题阐释,其指导思想当源于朱子的童蒙教化,理论核心来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其类聚范畴的形式当源于程子的“类聚言仁”说,但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与朱子的理念相偏离的,首先是孤立的抽离若干范畴加以训释,背离了虚心涵咏本文的理念。其次,对文本的阐发放弃了文字义的考察、抛弃了朱子非常看重的章句训诂之学。这样得出的义理,朱子恐怕是不放心的。真西山试图将字义与传统注释体结合起来,即是为了矫正字义体的干枯、单薄之弊。客观而论,“字义体”作为研究、阐释理学、四书的一种特有形式,对宋明理学的发展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亦比较有限。
总之,朱子门人后学将理学范畴与四书诠释相结合所创造的“字义体”,从形式和内容上皆对理学范畴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诠释,是对朱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使得理学与四书进一步融为一体,四书几乎成了理学的专属,理学亦借助四书而得到更合法广泛的传播。深入研究理学“字义”,对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理学研究、四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节 勉斋《中庸》学对朱子的接续与发展
朱子《中庸章句》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庸》诠释系统,主导了后世的中庸学发展。其高弟黄榦以创新之精神,在《中庸》章节之分、义理建构、工夫系统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赞为“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①勉斋将《中庸》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指出道之体用乃贯穿全书之主线,提炼出以戒惧慎独、知仁勇、诚为脉络的《中庸》工夫论系统,并深刻影响了弟子饶鲁、后学吴澄的中庸学,形成了《中庸》学上独树一帜的勉斋学派。富有开创性的勉斋《中庸》学虽寂然无闻,然其上接朱子,下开饶、吴,对宋元朱子学的《中庸》诠释实具继往开来之意义。
一 章节之分
勉斋据自身对《中庸》的理解,对《中庸章句》的章节之分做出了调整,朱子章句分《中庸》为三十三章,三大节。勉斋提出应分为三十四章六大节。他的《读中庸纲领》(小字:分六段授陈师复)详细阐述了他的想法(引文括号中文字为笔者所加):
(第一节)天命之谓性止万物育焉。此一篇之纲领。(1章)
(第二节)仲尼曰止圣者能之。此《中庸》明道之体段,惟有知仁勇之德者为足以尽之。(2—11章)
(第三节)君子之道费而隐,止十九章之半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言中庸之道无所不在,无时不然。(12—20章半。按:十九应为二十之误,“不明乎善”属20章“哀公问政”。如勉斋认为该章当为19章,应有所交代、提示。)
(第四节)诚者天之道也止纯亦不已。道皆实理,人惟诚实足以尽道。至此,《中庸》一篇之义尽矣。(20章下—26章。据勉斋“十九章之半”说,他把“哀公问政”章分割为上、下章,分属于第三、四节,可见他此处较《章句》多分出一章,即21—27章。)
(第五节)大哉圣人之道止孰能知之。此后六章,总括上文。一篇(疑为“节”之误)之义以明道之大小,无所不该,惟德之大小,无所不尽者,为足以体之。中间“仲尼祖述尧舜”,再提起头说,仲尼一章,言大德小德无所不尽者,惟孔子足以当之。此子思所以明道统之正传,以尊孔子也。至圣者,至诚之成功,至诚者,至圣之实德,此又承上文称仲尼而赞咏之也。(27—32章,即28—33章。)
(第六节)《诗》云“衣锦尚絅”止无声无臭至矣。末章言人之体道,先于务实,而务实之功有浅有深,必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息”而后已,至此,则所谓“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之谓也。(33章,即34章)①
可以看出,勉斋对《中庸》前三节的理解基本同于朱子。朱子对首章的阐发受到勉斋的推崇,《章句》引杨时说指出首章为“一篇之体要”,勉斋亦以“一篇之纲领”述之,认为此章言简意赅,包括本原、工夫、效验三方面,“此一章字数不多而义理本原,工夫次第,与夫效验之大,无不该备。”②勉斋对第二大节看法亦与《章句》基本相同,《章句》认为本节主旨是知仁勇三达德,“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余见第二十章”。①勉斋对第三节的看法亦与《章句》同,认为本节阐明了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费隐章对道的存在流行作出了极其显著的揭示,学者于此对道应当有所领悟,否则即是为文义所束缚,而无法见道。“看《中庸》到此一章,若无所见,则亦不足以为道矣。充塞天地间,无非是理,无一毫空阙,无一息间断,是非拘牵文义者之所能识也。”②《章句》亦认为本章主旨是阐发道之流行,呼应首章道不可离,统领以下八章。“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③
勉斋分章与朱子最大不同是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朱子认为,本章内容丰富,实为承上启下之章。上承前舜文武周公数章,阐明圣贤所传道统的一致性,对诚的论述则下启此后各章主题,故本章所述具有某种综合性,兼道之体用、大小,以呼应本节之费隐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举而措之,亦犹是耳。盖包费隐、兼小大,以终十二章之意。章内语‘诚’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④尽管朱子特别提到本章所论之诚,乃全篇枢纽,下文皆以诚为重点,但他仍然认为,对诚的阐发亦当置于道的背景下,没有必要单独突出、独立。这一点勉斋与之不同。本章历来是《中庸》诠释争议的焦点,朱子当时即因此与吕祖谦、南轩等往返辩难,朱子去世后,承担传道重任的勉斋仍在此问题上产生异议,可见勉斋“不唯朱子是从”的为学态度。勉斋对此章亦抱有极高评价:
哀公问政一章,当一部《大学》,须着反复看,榦旧时看,越看越好。⑤
此章语极宏博,其间语意若不相接,而实伦理贯通,善读者当细心以求之,求之既得,则当优游玩味,使心理相涵。则大而天下国家,近而一身,无不晓然见其施为之次第矣。①
勉斋将本章与最为朱子重视,被视为整个儒学纲领的《大学》相比,认为其内涵丰富,义理精密,深厚含蓄,故须反复熟读体会,方能见出其义理无穷。就本章文本论,其用语广大,所论话题似乎时有跳跃,缺乏内在的连续整体性,但其内在思想则明畅条达,精密有序而互为贯通。故须以精细之心来探究之,在求得内在文义基础上,再从容涵养、反复把玩,体会咀嚼其味,最终达到心理相涵,融化为一的境界,如此则可进乎内圣外王之道。勉斋所强调的是,本章不仅阐释了明德修身之方,而且论述了新民治国平天下之道,义理无穷,足与整部《大学》相比。
勉斋将本章划分为上下两章,且分别归属第三、四部分,其用意很明显,就是突出“诚”的地位。下章自“诚者天之道”始,与“诚明”“至诚尽性”“曲能有诚”“至诚如神”“不诚无物”“至诚不息”章构成了以诚为中心的第四部分。他认为《中庸》一书,至此为止,其意义已经穷尽。“至此《中庸》一篇之义尽矣”。也就意味着,在前面分别论述一篇纲领、三达德明道之体段、费隐明道之普遍存在后,至“诚以尽道”,乃是《中庸》全部意义所在。
在大节之分上,勉斋与朱子最大不同在于是否将诚独立为一个单元。《章句》视哀公问政章为一个整体,归于费隐节。自诚明章以后直至篇末,统为一大节,其主旨乃是天道、人道,“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②。这种安排显然并没有特意突出“诚”而是强调了“道”,认为诚内在于天道人道中,乃是道的应有之义。这亦表明朱子是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中庸》全书的,自有其合理性,在《中庸》是一篇还是两篇的质疑中,这种安排很好地保持了《中庸》一书的内在完整性和一体性。①
勉斋以六章篇幅构成以“诚”为主的第四节后,又将“大哉圣人之道”以下六章划为第五节,这亦与朱子不同。勉斋认为本节与上节关系密切,是对上节诚论的总结概括,是论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只有穷尽德之大小,无所不至者方能体道,乃是围绕道、德两个概念展开。前三章是论道之大小,后三章以仲尼为例论证德之大小,与天相合,《章句》则认为前三章是人道,后三章是天道。
勉斋将最后一章独立为一节,引《诗》论述体道工夫及其高远境界。本节与首节独立与否并不对全书结构产生大的影响,故很多朱子学者亦倾向于将首、尾两节独立出来。勉斋曾对《中庸》下半段关系有一整体论述: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间又怕人做得不实,“诚者天之道”以后,故教之以“诚”。后面说“天下之至圣”,是说其人之地位,“至诚”是说其人之实德,到“衣锦尚絅”以后,又归“天命之谓性”处,此四段最好看。②
勉斋认为,《中庸》前面是有关工夫论的讨论,如三达德等,接着费隐一节又担心人工夫实践不真实,故自哀公问政章的“诚者天之道”后,开始论“诚”。天下至圣、至诚章分别论述圣人之地位和德性,末一章则重新呼应首章“天命谓性”说。可见,在勉斋看来,《中庸》以论诚为界限,似乎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面以戒惧慎独、三达德工夫为中心,包括第一、二、三节;后面以诚的境界为中心,包括第四、五、六节,而他认为自“诚”论一节后,“《中庸》一篇大义尽矣”,正表明此意。
二 道之体用《读中庸纲领》对各节的概括显出勉斋从道的角度论述中庸。如第一节言道之纲领,第二节“明道之体段”,第三节言中庸之道无所不在、无时不然,第四节论“道皆实理,人惟诚实足以尽道”,第五节明道之大小,第六节言人体道之境界。勉斋曾讨论学习《中庸》的方法,他以程子、朱子说为基础,得出以体用论中庸之道的思想。在《中庸总论》中给予了详尽阐发:
苟从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先生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①
《中庸》一书具有不同于《论》、《孟》的特点,故从总体上通晓全篇旨意,较之具体的章句分析更为重要,程子理事说、朱子诚之枢纽说,精密、确切的点出了全篇要旨,是学习《中庸》之指南。勉斋由此进一步提出道之体用说:
窃谓此书皆言道之体用、下学而上达、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与道,则性为体,而道为用矣;次言中与和,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矣;又言中庸,则合体用而言,无适而非中庸也。又言费与隐,则分体用而言,隐为体,费为用也。自‘道不远人’以下,则皆指用以明体;自言诚以下,则皆因体以明用。大哉圣人之道一章,总言道之体用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之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尽道之体用也,大德敦化,道之体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用即体,体即用,造道之极致也。虽皆以体用为言,然首章则言道之在天,由体以见于用,末章则言人之适道,由用而归于体也。②
首先,《中庸》全书皆围绕道的体用展开,体用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书中很多重要概念即具有体用相对关系,如性与道、中与和、费隐,中庸则体用兼具。全书文本结构的内在联系亦为体用关系,如“道不远人”章以下,是“指用以明体”,“言诚以下”则反过来,“因体以明用。”此是受《章句》影响,朱子认为“道不远人”章所论,“皆费也,而其所以然者,则至隐存焉。”“诚则明”章是论述天道、人道,此后12章,皆反复交错论及天道、人道这一主题。但勉斋不认同此说,《章句》认为“大哉圣人之道”章是“言人道”,勉斋指出是总言体用;对认为是言天道的仲尼祖述及以下至圣、至诚章,勉斋则认为仲尼祖述章是言圣人尽道之体用,至圣、至诚则是分别全道之用、道之体。勉斋还认为,末章是论体用为一的最高境界,首章命性之说,是由天到人、由体及用,末章则是由下学上达,以人达道,由用归于体。二者首末恰相呼应,体现了体用概念对全书的贯穿始终。
其次,分析《中庸》论道之体用的四个原因。
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知道有体用,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知道之有体,则凡术数词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则虚无寂灭,非道也;知体用为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体用合一,则从容中道,皆无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①
如果知道有体用两面,则可以实现日常动静之间,达到自然纯乎天理而人为私欲的境界;则可以辨析小道、异端之学的不足,或有用无体、或有体无用。一方面,既知道之体用是有分别的,则须始终于操存省察之上用功;又知道之体用又是合一的,体即用、用即体,故有自然从容的中道境界。中庸以体用论道,实现了对道的最高论述。既然如此,为何孔孟不言体用而子思言之?孔孟何为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学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体,恕即用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非道之体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传之子思也。孟子曰……恻隐羞恶辞辞逊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传之孟子也。道丧千载,濓溪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其言太极者,道之体也;其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道之用也。……圣贤言道,又安有异指乎!①
勉斋就孔曾思孟周子的道统传承立场论述了道之体用。曾子得自孔子的忠恕,即道之体用,“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曾子传给子思的道之体用,孟子四端说是得自子思的道之体用。道丧千年之后,濂溪以太极、阴阳说重新接续道之体用说。可见,道之体用为儒道之核心内容,是一直传衍不息的。
勉斋进而解释了三个问题,一是天人体用的分合关系。
或曰:以性为体,则属乎人矣。子思……乃合天人为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②
勉斋以太极说来解释之。指出性来自天,是理、体,同时又为人禀受,则转为人之用。天人无间,人所具有者本源于天,统体于太极,天下万物皆在性理之内。反之,万物各具一太极,故在天者,同时又内在于人,此为天人合一、体用一如也。
二是体用之分与程子性气、道器之合的冲突。或曰《中庸》言体用,既分为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气、气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则何以别其为体用乎?曰:程子有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也”。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类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色、天性之谓是也。①
勉斋以程子体用一源说进行解答,指出分合不同之解,乃是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故当灵活观之,其中并无不合。从理的角度论,则体始终包有用,并未脱离用而独立存在之体,如程子冲漠森然之说即是此意。从物的角度言,则用始终内在具有体,没有脱离体的用,如《易》之阴阳即是道,《孟子》形色即天性说,即是指出体用之合。
其三,既然体用不离,又如何区别费隐?
如此,则体用既不相离,何以别其为费为隐乎?道之见于用者,费也;其所以为是用者,隐也。费,犹木之华叶可见者也,隐,犹华叶之有生理不可见者也。小德之川流,费也;大德之敦化,隐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体用之未尝相离也。嘉定戊寅栖贤寺书此,以为《中庸》总论。②
勉斋指出,费为道之发用,隐为用之根源。费是显现于外的可见之花叶,隐是潜伏于内无法目睹的生生之理,此见体用二者有别。大德敦化与小德川流分别为隐、费,但又互相包容,彼此相涵,可见体用又未尝相离。勉斋不仅以体用为中庸之道的根本,而且视为他对儒家之道的根本体悟,反复以之来详尽剖析《中庸》。他在《复叶味道》书中说:
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间只是一个道理也。①
道在天下的呈现,无非是体用而已。体只有一个,用则是无数,体用是一多关系,是理一分殊。《中庸》开篇性道即是一本万殊关系,大德与小德亦然。他将之与朱子的《太极图说解》紧密结合,语大是一本万殊的万物统体太极,表明性外无物;语小是万殊一本的一物各具太极,指性无不在。从性的普遍视野看,万物皆同,正因万物之理皆同,故只要存心、把握住固有良心,则事物之理无不具备,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义。自道的分殊角度,万物各异,故需要事事逐一穷理,以达到万物之理的贯通。故圣贤或就道之体的理一言,或就道之发用的分殊言,说虽不同,义则为一,皆言道之体用也,此乃为世界普遍共有之理。
勉斋对体用说的论述是以朱子《太极图说解》的“统体太极、各具太极”说为基础的,由此悟出体用的分合、兼统关系、他指出当以朱子太极统体各具说与《中庸》尊德性、道问学注比照合观,一方面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各自兼有体用,但二者之间却是统体为体,各具为用。语大、语小虽然皆是指用,但二者当以语大为用。天命谓性与率性谓道、大德与小德关系亦是如此。可见体用是相对言的,有自身之分体用,又有以相关对象相较的体用。更取朱先生《太极图解》以“统体太极为天下无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极为性无不在”之语,并《中庸》尊德性道问学注观之,不知如何?……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底又是体,各具底又是用。有统体底太极,则做出各具底太极。①
三 “戒惧慎独知仁勇诚,此八字,括尽《中庸》大旨”
在《中庸总论》中论述道之体用时,勉斋即提出求道工夫的问题,他认为戒惧慎独、知仁勇、诚八字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工夫,也是全书大旨所在。“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巳,是则一篇之大旨也。”②为此,他专门撰有《中庸续说》一文论述之。
至于学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复包罗而极其详且切焉。……首言戒惧谨独,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无不善者而为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简而易行,学者于此而持循焉,则吾之固有而无不善者,将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末言诚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见天下之理无不实,欲人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③
子思对如何用功,反复论述,极其详尽切当。首章提出戒惧慎独工夫,针对性、道本为人所固有而纯善无恶,故工夫在于防止未然之不善的侵蚀而审察所以然,此工夫具有易简特点,只是自然而发的当下一念。“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实质是静时存养、动时审察的动静不离工夫,以此实现性道的当身存在。知仁勇三达德,乃针对克除气禀、物欲而发,需要明知、力行、勇猛工夫,以保持固有之善,实质是知行并进工夫,以做到由体至用的展开,皆合乎中庸。最后言诚,针对天道、人道之分,天理本是真实无妄的,故人当真实用功,以保全真实无妄之天理。它始于择善固执工夫,终于无声无臭。
勉斋认为,《中庸》对此八字工夫有着详切论述。
戒惧谨独者,静存动察之功。能若是,则吾之具是性而体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则由性以达夫道者,举合乎中庸而无过不及之差也。曰诚者,则由人以进夫天,圣贤之极致也。是非其言之极其详乎。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谨独于至微至隐之中,则所谓静存动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继之以仁,曰仁矣而继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则所谓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诚也,本于择善、固执之始,而成于无声无臭之极,盖至于所谓大而化之,过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岂非又极其切者乎。若不极其详,则学者用心或安于偏见;不极其切,则学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忧虑天下后世而为是书也。①
戒慎工夫的实质是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如能做到此,则能实现天命之性、体验率性之道。知仁勇则是知止力行工夫,如能做到此知行工夫,则由天命之性落实于率性之道过程中的种种行为,皆能合乎中庸之道。诚则是下学上达、由人而天的圣贤最高境界,即此已显出《中庸》论述之详尽。“戒慎不睹不闻、谨慎至微至隐”显出静存动察工夫之紧切;言知而紧接以仁、勇,可见致知力行工夫之紧切;言诚而始终于择善固执、无声无臭,又见其紧切。之所以如此详细紧切,是为了防止学者安于偏见、止于小成。此八字工夫事关道之传承,故对之加以极切阐释,就成为子思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勉斋反复指出,此三节八字工夫次序丝毫不可紊乱,先是戒惧,其次知仁勇,最后是诚,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始于戒慎,紧接的知仁勇则是对戒惧的实行,知仁勇又需要守住其诚来加以落实。但反过来讲亦然,戒惧的实行须先之以知仁勇,知仁勇的实行又以诚为前提,故最终又落实于戒惧慎独。工夫可谓终始于戒惧。
始之以戒惧谨独,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终之以诚之一字。①
《中庸》一书,第一是戒谨恐惧,然戒谨恐惧亦须是先有知仁勇以行之,然知仁勇固所以行之,又须是守之以诚后可,其终又归于戒谨恐惧。此《中庸》之大略也。②
戒惧可谓三节工夫之核心,对此工夫时刻不可离开,是工夫主干所在,知仁勇是具体做知行工夫,包括读书穷理,诚是对工夫的最后实现,有此则工夫完满无遗,它兼有工夫与形上义,尤其是全书后面,至诚诸说的形上境界义极其突出。如上文所引,勉斋认为全书至第四节“诚”论,已穷尽一篇之义,即居于此工夫论立场而发。“《中庸》戒惧慎独是大骨,顷刻不可忘,知仁勇是做工夫,读书讲明义理,后面着个‘诚’字锁尽。”③
在给饶鲁的信中,勉斋对此八字评价更高,认为不仅是《中庸》大旨所在,更是囊括穷尽了千古以来圣贤的教法。
《中庸》之书首言戒惧谨独,次言智仁勇,终之以诚,此数字括尽千古圣贤所以教人之旨。戒惧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谓也;谨独以致乎和者,集义之谓也;致中和,岂非检点身心之谓乎。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过求所以致夫中和也。如此而加之以诚,则真知实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学者立心,便当以持养省察为主,至于讲学穷理,而持养省察之意未尝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义愈精矣。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皆务外者也。①
勉斋从两方面来论证此点:其一,将戒惧、慎独与致中和、居敬、集义等重要工夫对应起来,戒惧是居敬,是致中工夫、慎独是集义,是致和工夫,故致中和不过是检点身心之学。知、仁、勇则是达到致中和的途径,于此基础上再贯注以诚,则能做到真知实行、勇猛不懈。居敬是把持养护此心,集义是反省审察此心,故此八字工夫无非是持养省察、检点身心。其次,将戒慎工夫与讲学穷理比较论之,强调为学当以戒慎存养省察为主。如上所述,戒慎是八字工夫“大骨”,故常以之为工夫代表。为学以戒慎还是讲学为主,直接关系到为学方向是切己向内还是务外为人。勉斋直接批评了凡是不以戒慎为工夫之主而只知讲学穷理者,皆是务外之学。因戒惧慎独终身事业,故不可有丝毫放松,讲学穷理不过是讲明道理使之不误而已,并未进入到实践层面,只能起到工夫的辅助作用,“须是如中庸之旨,戒惧谨独为终身事业,不可须?废,而讲学穷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勉斋以戒慎、知仁勇、诚作为工夫要领,一方面是在《章句》影响下提出的,如静存动察来自《章句》“存养省察”说,认为自“君子之中庸”章开始言知仁勇,诚字因天道、人道之分,皆来自《章句》说。朱子认为从诚明章开始以下十二章,皆是自天道、人道反复论说。另一方面,又是勉斋的独特体会和创新,通过对戒慎、知仁勇、诚的三项工夫的突出,使得原本以形上学、深奥著称的《中庸》有了一条非常简洁清晰的工夫线索,是对朱子《中庸》工夫论的概括和提升,也是对《中庸》诠释的重要补充与深化。
四 双峰、草庐对勉斋中庸学之传承
勉斋中庸学确有“发朱子之所未发”处,并深刻影响到后世朱子学。其弟子饶双峰、双峰再传吴草庐亦皆对之作了新的继承阐发。总体看来,双峰受勉斋的影响很明显,二者可谓大同小异,但这小异却影响甚大。
在章的划分上,双峰亦将全书划分为34章,亦将“哀公问政”章一分为二,但在具体划分上却与勉斋有所不同,他根据“哀公问政”至“不可以不知天”为孔子之言的依据,将之划为一章,即第20章;自“天下之达道”至章末“虽柔必强”是子思推衍孔子之意所成文字,另划为一章,即21章。深受双峰影响的草庐在《中庸纲领》中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干脆将哀公问政章拆分为四章,并独立为一节,刻意突出该节的特殊地位,其主旨为“论治国之道在人以行其教”而非诚。在大节的划分上,双峰与勉斋亦有同有异。同者,皆分为六节,皆将第四节单列为诚,差别仅在于对哀公问政章的处理,双峰尽管亦一分为二,却皆归入第四节“诚”论,勉斋则分别归于三、四节,如此,本节双峰较勉斋多出“哀公问政”一部分。在各节主旨及其关系认识上,双峰颇有创见。他以简明扼要之语概括了各章要旨:首章中和节,2—11章的中庸节,12—19章的费隐节,20—28章的诚节,28—33章的大德小德节,末章的中和节。特别是指出全书是一个具有高度联系的有机整体,各节之间彼此照应,首、末两章皆自成一节,中间四节则是两次开合。第一次开合是由中和而中庸而费隐的打开,再由费隐而诚的闭合。第二次开合是由诚而至道至德的放开,再由至道至德到末节无声无臭的合拢。两次井然有序的开合显示了《中庸》结构的完整性和节奏性。①双峰之六节说影响盖过勉斋,得到后世主流朱子学者的认同,而勉斋之说几乎湮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恐与双峰对各章节关系的精密论述有极大关联。②
如果说双峰是在勉斋基础上“后出转精”,那么草庐则显然更有针对双峰的意味,他受双峰思想深刻影响是无疑的,数次提及对双峰《大学》、《中庸》的看法,批评双峰章句说过于分析。他在《中庸纲领》中将全书分为七节34章,在章的划分上,他对朱子《章句》采用了合并、拆分法,颇不同于前人。把《章句》22章“唯天下至诚尽性”与23章“其次致曲有诚”合为一章,构成他的25章;把“不诚无物”章与“至诚无息”章之“故至诚无息”至“无为而成”部分结合起来组成他的27章,而“至诚无息”章剩下部分“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以下则单独组成28章。在节的划分上,除将哀公问政章独立为一节,首节、次节、第3节、第七节与前人相同,差异在于把24—30章划分为明诚、圣天一节,突出“诚”在全书中的中心地位。且把31、32、33章划为第六节,论孔圣之德与天为一。列简表如下:勉斋、双峰20/21章为朱子《章句》20章哀公问政章之拆分,具体所分有所不同;草庐一行,括号中为朱子《章句》之分,但草庐四、五节的各章之分已与朱子不同。①
关于《中庸》主旨,勉斋认为《中庸》是论道之书,尤其阐发了道之体用说,双峰亦明确提出,“《中庸》一书大抵是说道”,突出了中庸之道与物不杂不离的双重特点。勉斋对《中庸》三项工夫的阐发,在双峰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回应和阐发,双峰认同朱子、勉斋的戒慎解,“戒惧,存养之事”“慎独,省察之事”,但亦有新的理解,对《章句》颇有批评。特别突出了第二节“中庸”节所体现的变化气质的自修工夫,突出了知、仁、勇的重要性,认为“《中庸》大抵以三达德为体道之要”①。饶鲁认为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五句当以首句为纲,其余四句为目,皆言道问学之事,提出了尊德性在其中的主干地位,还提出了“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这一带有浓重心学意味的命题。②这一看法得到草庐的认同,并获得进一步弘扬,草庐强调以尊德性为主体的情况下来展开道问学,力求兼顾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尊德性为体,道问学为用,二者具有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并由此被视为元代朱陆合流的代表。③
综上所述,勉斋在《中庸》分章、主旨、工夫论方面皆对朱子《章句》有所改造和突破,形成了自成一派的《中庸》学,并得到后学双峰、草庐的进一步推阐,尤其是双峰的章节之分,更是成为后世理学中有代表性的见解,显示出勉斋学派的创新能力。元人程钜夫已经道出此点,他说,“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双峰之说,又有勉斋所未及者。”令人奇怪和遗憾的是,双峰、草庐的《中庸》学皆有相当之影响,作为二者源头的勉斋《中庸》反而默默无闻,不为学界所熟知,一冷一热适成对比。勉斋著作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属《论语通释》,该书虽已散佚,但许多重要条目皆为宋元以来诸家《四书》所引述,影响甚大,至今不绝。这与其《中庸》学之冷遇又成比照。事实上,勉斋《中庸》学确实卓然成家,其所开创的《中庸》学派,以其有守有为的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庸》学的诠释和朱子学的向前发展,其思想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节 美国当代朱子《四书》研究:以贾德讷为中心在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亦须具备全球视野,方能整体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即以儒学研究为例,如何突破“东亚化”,实现“全球化”已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走向。近年来,国内的朱子学和四书学(包括东亚四书学)研究非常活跃,但对英语学界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关注不多。①本文拟对英语学界相关成果加以评述,以为国内朱子四书学研究提供借鉴。美国贾德讷(Daniel K. Gardner)师从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始终坚持对朱熹四书学的翻译、研究,先后出版了《朱熹与〈大学〉:新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反思》、《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朱熹对〈论语〉的解读:经典、注释与经学传统》、《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②贾氏的研究以对朱熹《四书》文献的翻译、注解为基础,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中国经典学的重要问题,如经典与理学、经典与注疏、经典与教化、学以成圣等。这些论题亦为当前中国学界关切所在,故甚有必要对贾氏的研究加以论述。
一 朱熹《四书》与理学
与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常用进路不同,贾氏基于对理学与经典内在共生关系的认识,选择从儒学经典切入展开理学研究。他在《朱熹与大学》序中提出,英语学界尽管对新儒学有了各种研究,但几乎无人关注新儒学和儒家经典的关系。这种不幸忽视鼓励了早在宋代就被新儒家反对派提出的观点——新儒学学说的产生几乎与儒家传统经典无关,更多地来自佛学而非儒学。作者对此予以鲜明反驳,强调本书的核心就是要矫正过去对儒家经典的忽视,确信宋代新儒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深的敬意,并从中汲取灵感。①故贾氏的研究始终关注经学与理学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贾氏认为儒家思想离不开经典。儒者在寻求灵感和指导时求助于被认为包含了儒家思想基本教导的经典文本。读经不仅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义务,更是一种参与古代圣贤对话的方式。四书取代五经原因虽多,最根本的则是对佛教的应对,这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本体论。与五经相比,《四书》更集中关注人性、道德的内在根源、人与宇宙关系问题。贾氏虽亦认同新儒学受到佛教刺激,但其思想的根基却在于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其资源主要来自被重新改造了的儒家经典《四书》而非佛学。故贾氏直接投入于作为新儒学核心资源的朱熹《四书》,从儒家经学史立场来看待新儒学。
他强调从对朱熹《四书》文本的研究中察知新儒学和经典的关联。在所有新儒家中,朱熹与经典联系最紧密,其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的发展是复杂的辩证关系,朱熹走向经典解释正基于其新儒家哲学的核心信念。②他基于自身的本体论假定人皆有能力对经典作出有意义的思考。
之前的学者也相信过去圣贤在儒家经典中传达了真理,但朱熹与他们的差异在于在文本中追寻何种真理。宋代之前的经典学者普遍寻求有限的限定真理,即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境遇,如何给出最有效管理民众的处方;而朱熹则是在寻求一个普遍真理——宇宙中既内在又超越的一个真理。③自此,儒家经典不再是指示性的,而是体现了宇宙中包含一切的普遍之理,这个理将会向任何读者显示。当然,朱熹认为文本中的真理并不易获得,因为没有任何词语能完全表达圣贤的深刻含义。
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阅读》的诠释中,论述了朱熹形上学及经典诠释的几个特质。他指出“我欲仁”章朱注采用了本体论的信仰,使孔子的评论完全明白易懂,把握了《论语》个别篇章与更大传统的关系。朱熹根据孟子的人性论观点来论证本章:一方面经典文本的认同给了这段《论语》更深的共鸣和更连贯的意义,同时加强了《孟子》立场的合法性和意义。最终使得把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变得更有说服力,孟子人性先天本善的观点也显得更自然和更权威。这都说明朱熹的注释起到了联接文本自身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儒家更大传统的中介作用。①他又以“性相近”章为例提出朱熹的《论语》文本和形上学之间关系是动态的:形上学阐发了《论语》的教义,教义使得形上系统富有意义。这种教义与奠基于形上基础的注释的相互交融使它们根本兼容,反过来给形上学一个“儒家”的有效性和意义。
二 朱熹《四书》与经典诠释
贾氏认为儒家经典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典的面貌实际上又由注疏塑造。儒家通过行间注释来表达对圣贤之言的理解和自身哲学思想,经典注释成为追随儒家之道的主要哲学表达模式。②他根据经典诠释方法的差异划分经学史的发展阶段,显示出独特的视角和对经学诠释方法的重视。指岀宋代有三种经典研究方法:考据性(the critical)、经世性(the programmatic)、哲学性(the philosophical)。第一种探究经典文本、注释的著者及其真实可靠性。第二种关注经典中的古代制度、系统或道德价值,讨论其对现实环境的可运用性。第三种是宇宙论解释,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或人道德的内在性。此三种方法乃包容而非排斥关系,他据此对汉宋经学作了发展阶段的区分。第一阶段始于中唐至北宋,考据性方法流行;第二阶段为北宋初期,考据性方法继续流行,经世性方法发展起来;第三阶段是方法多元性时期。前两种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同时逐渐出现哲学性方法,以周敦颐为代表。第四阶段表现为哲学方法的唯一性,《易经》和《四书》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以张载、程氏兄弟为代表。第五阶段是宋代经典解释的成熟和综合期,这一舞台被朱熹主导。③
他又认为,当今儒家经典主要有历史和哲学两种解经方式。一种是通过广泛的文献考察来发现、重构作者试图在文本中表达的意图,另一种是非历史的、哲学的解读方法,试图寻找文本中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内容:即文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作者的《朱熹与〈大学〉》一书采用的就是其一贯的历史学方法,它首要关注的是文本是如何被理解及为何作出这种理解,而不关注是否应当作这种理解——优先关注事实解释而非价值判断。尽管所有的经典解读法都是合法的,但却指向不同目标。历史方法的解读试图至少揭示出中国过去儒家传统的动态发展。其基础是相信儒家文本的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解读者眼里是不一样的,故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思考不同于郑玄等汉代儒者是很正常的。
历史性与哲学性注疏的比较。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中着眼于研究视角和诠释方法,以朱熹、何晏对《论语》的注释比较为例,具体阐明了儒家经典是如何被加以不同诠释的。就诠释视角论,何晏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朱熹则从伦理和哲学的角度。与何晏不同,朱熹直接在注疏中发表看法,引导读者,认为读者不仅应当理解文本的意义,更应明白文本的普遍应用性。①如“礼之本”章,何晏的注释仅仅是重复夫子的话,是描述性的,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相反,朱熹的注释在篇幅上通常比经文长很多。朱熹认为,夫子的评论被弟子组织起来构成《论语》一书,成为一个有深层内在连贯意义和洞见的文本。这一点对朱熹来说几乎是一种信仰。②朱熹认为通过对圣人之言的持续研究、体验,他已经完全获得了这种洞见。这种对文本真理的理解、洞见对所有人也是敞开的,只要他们愿意为此努力投入。他的注释就是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一种帮助,向他们揭示自己有本在文本中已发现的真理。
贾氏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诠释者的角色和目的;如何根据自身思想来重塑《论语》。自我角色定位就是如何理解注释者与文本、传统、读者的关系。在何晏那里,前辈之说具有完全的权威性,在朱熹这里,只有二程等支撑其观点时才有权威性,在经典、权威、读者的三层关系中,他将自己置于整个对话的中心。何晏在诠释中尽量少地“发声”,朱熹则相反,原因在于朱熹的态度是传教灌输式的(proselytizing attitude),带有某种论辩性。这种对《论语》文本深刻的,几乎是宗教义务性的态度清楚解释了朱熹艰苦的注释努力。对朱熹来说,《论语》的价值在于对人具有深刻的转化作用,正是这种对《论语》权威和效果的信仰促使朱熹穷毕生之力注释《四书》。①他的注释尽力使读者相信儒家传统在宋代仍然是有生机和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信仰辩护(as an apologetic)。他认为把《论语》塑造到一个对当代读者有意义的传统中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需要使读者相信孔子的教导和他们的世界是相关联的。朱熹通过对经典的自我反思,自信有能力把握圣人原意,确信他的心与圣人之心已经变为一个。②朱熹确实已经获得了对理的彻底理解,进入了圣贤之境,圣贤之意已极其清楚 地向他显现出来。朱熹和何晏在《论语》中表达了不同的形上系统,决定了他们对圣贤之意、对道的理解的差异。
篇内连贯和文本互涉(intra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references)。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主要探究了行间注的体裁,突出了它在中国知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作用。③自汉代始,行间注便成为主要写作文本形式,该书试图探究以下论题:朱熹为何采用集注形式?如何理解注者和文本的关系?如何协调过去圣贤之言与当代读者的信仰、约定?朱熹的注释如何形成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它如何受到早期注释传统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此后 《论语》的理解?该书通过对何晏《论语集解》与朱熹《论语集注》的翻译、分析,阐明经典文本和集注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作为知识表述的一种工具,行间注不是简单的去文本中发掘灵感和意义,而是同时给予文本意义,极大地构成和重构了对文本的阅读。贾氏从《论语》中挑选了学、仁、 礼、政、道、君子等直接内在关切于儒家核心思想的篇章,以突出朱熹极大改变核心文本意义的方式,显示行间注理解对把握中国传统是如何关键。
贾氏指出,假定文本是一个内在整体是朱熹所有注释重要而鲜明的特质。朱熹认为儒家经典是一个内在综合的整体,每个部分都给整体以意义,正如整体阐明部分一般。这种融合贯通的努力深化了《论语》文本的经典性,特别是强化了四书的核心性,通过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对于愿意倾听者来说,它是开放的,可以进入的。如“博施济众”“十室之邑”“三十而立”等章充分体现了朱熹文本互涉的诠释特征。这种方法给予每种文本合法性,在突出文本内在关联和一体性的同时,还使得彼此更加好懂。著者以《论语》中关于“仁”的9章为例,指出朱熹的评论促使读者依靠整个《论语》及其注释的相关背景去阅读《论语》,这种整体性、一致性是何晏注所没有的。朱熹甚至超越了《论语》文本自身,使夫子的语言纳入更大的儒家哲学视野。著者指出,何晏与朱熹对克己复礼理解的重大差异在于前者认为礼产生了仁,后者则主张仁产生了礼。这种差异在美国学者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和史华慈的争议中同样体现出来,前者的主张近乎何,后者近乎朱。
三 朱熹《四书》与德性教化
通过经典来推行教化是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根本任务,贾氏非常关注此 点。他指出宋代思想发生了由外王至内圣的“内转”,在此转变过程中,朱熹的最大贡献是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对 《大学》的理解发展出来。①朱熹对《四书》的重视超过五经是因为他认为《四书》体现了道的本质。在《四书》中,《大学》应最先学习,它比任何一部儒家经典都更简洁地表达了儒学之道的广阔目标:个人修身和社会治理。朱熹对《大学》个人式的、宗教性的解读(this sort of personal, religious approach to the Ta - bsueb)导致对文本全新的理解,与传统上对经典理 解相比,至少有三方面重要突破:首先,汉唐学者主要把《大学》理解成仅为统治者使用的政治手册,朱熹将之看作所有人自我修养和社会治理的指导,扩大了《大学》的读者范围。其次,朱熹发现了《大学》里面的一个 本体论假设和自我修养过程后面的目标——明明德,朱熹认为明德不是向外展现德性或德性行为,而是内在道德心或每个人降生之初的天赋之性,它可能受到物欲或人欲的污染。贾氏认为其实朱熹的明德是包含了心性的一个整体。第三,朱熹认为《大学》规定了实现性的正确途径一格物,它被视为整个自我修养过程的第一步和基础。朱熹在格物补传中对此作了雄辩阐发,特别讨论了觉悟问题,他把格物作为儒家矫正佛教静坐的方法,它可以导向自我实现和升悟境界,同时又是自我与社会连接的中心。
学以至圣。贾氏所译七卷《朱子语类》的正标题是《学以成圣》,意在表明朱熹的中心关切是如何学以至圣,即道德上的充分实现。他的形而上学综合代表了儒家哲学的新发展,试图给人的道德完善这一儒家传统教学目标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对朱熹来说,人之天赋性同气异,气的量质将决定人性是呈现还是继续被遮蔽。朱熹对此给予了最多的哲学关注,给弟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系统、渐进的自我完善工夫,工夫程序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格物。格物是改善自我和本原道德之性的手段,是自我觉醒、回归真我的过程。
基于此,贾氏《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通过对《朱 子语类》中有关学的篇目译注来显示如何经由学习达到圣人境界。该书据清代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选择“为学”七卷加以翻译,详尽分析了朱子为学生设计的学习计划。诸如“学”为何意?何者为核心课程?如何学习文本?读者与文本关系如何?他认为与北宋学者相比,儒家发生了由确认一个有道德的人到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转变。①由传统的如何发现贤人转变为如何培养贤人,朱熹倡导《四书》作为核心课程,吸引学者更多地走向内转反思的精神生活,而非外在的政治参与。贾氏确定《论语》的第一主题是“学”,在比较何晏、朱熹注释差异时指出,何晏的“学”仅仅是对合适文本的诵习熟读,朱熹的“学”则带有明显的道德目的。②
贾氏在《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中提出,朱熹尽力于《四书》就是要解释孟子提出的两个哲学问题:如人性为善,恶从何来?如人性为善但如何实现之?朱熹对人性内在潜在之善与实际行为之善存在的鸿沟加以精致的哲学化解释,其哲学系统就是将自我修养过程视为中心论题。要实现这种完善,意志和努力是根本的,格物又是工夫第一步。学习体验《四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服务于修身,通过修身使道德呈现于各种相互关联中,仁就是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Goodness' is to be good in one's relations with others .①仁的字形亦表明它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中获得。苦行者数十年坐在叙利亚沙漠里的柱顶来消除心中恶魔,以便在上帝眼里变好,这在儒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儒家认为政府具有一种最高权威,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来推进人民的道德发展。好的政府应当是有德行的,它的管理依赖于道德力量、礼仪实践而不是法律,这是儒家洞见的政治基石。《四书》支持的政府形式是一种仁慈的家长主义,统治者对民众有着如父亲对子女般真诚深厚的关心。在《四书》看来,理想的政府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道德命令,好的政府使人民变好。②这使得儒家的政治教义与其他大多数的政治哲学不同。但在《四书》中存在一个教义的循环,即政府好人民才会变好,但只有好人同意为政府服务,好的政府才有可能。故中国统治者依赖于科举来发现这样的人,这又依赖于对《四书》的学习。
四 朱熹《四书》与经典翻译
贾氏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翻译基础上,对《四书》相应术语的运 用体现出其本人的思考方向。以“经典” 一词为例,贾氏在论及儒家五经、十三经、《四书》时,采用了 Canon 一词,而在表达一般意义上的经典时,则采用Classico这两个词最根本的区别是Canon指“A collection or list of sacred books accepted as genuin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该词来源于基督教,常指《旧约》、《新约》,带有明显宗教意味。但是否能仅据贾氏使用该词来断定其对朱熹《四书》研究是从宗教学研究角度出发呢?贾氏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其一贯的研究方法是在《朱熹与〈大学〉》中已指出的客观、平实的历史研究法,以如实把握朱熹的经典思想。他的朱熹研究并无任何宗教意味,尽管他曾指出朱熹对《四书》研究的执著已带有某种宗教情怀,但只是意在表明朱熹的研究态度。作者使用Canon意在表明儒家思想系统中具有《圣经》般地位的经典已由五经转换为《四书》,以此突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经朱熹诠释后,已成为真正的Canon,影响统治了中国后期的知识史,非一般Classic可比。它所指的是《四书》的经典地位而非表明作者对朱熹研究的宗教态度,并不能以贾氏之书来证明西方朱子学研究的宗教性趋势。①
诠释的主观差异性与文本的客观同一性。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 读》一书以比照方式突出了何晏《论语集解》历史诠释与朱熹《论语集注》哲学诠释两种方法的差异,就《论语》何、朱不同注释直接给出不同翻译,区分了不同学者视域中的经文,达到了彰显朱子新经学与何晏经学不同的目的。
如:时习之,何:以时诵习之。recite it in due time;朱:时时习。re-hearse it constantlyo②与其易也的“易”。何:和易。serene.朱:易,治也。meticulous.③又如“有耻且格”的“格”,何:格,正也。Set themselves right.朱:格,至也。……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Arrive at good.④朱熹对,,格”的第一解为“至于善”,第二解则同于何晏。他曾明确表示,如两解并存,以第一解为优。
贾氏的翻译存在变易。19世纪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奠定了西方中国经典翻译的典范,他对《四书》的翻译亦以朱熹《四书》为底本,将贾氏对《大学》主要范畴的翻译和其译文相对照,可见出贾氏的特点。下文J指James Legge, G1指贾氏1986年版《朱熹与〈大学〉》译文;G2指其2007年版《四书:后期儒家基本教义》译文。
明明德:J : 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
G1 : keeping one's inborn luminous virtue unobscured
G2 : letting one's inborn luminous virtue shine forth 格物 J: investigation of thingso
G1 : apprehending the principle in things
G2 :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就字面意义对称而言,“明明德”两个“明”字只是词性不同,意义并无多少差别。贾氏的翻译过于曲折,不如理雅各精准。贾氏2007年译文较1986年在语义上更具积极性、主动性,但仍不够简洁。早期贾氏对“格物”的翻译,意译为“穷究事物之理”,亦不够恰当,若 此,则如何翻译“穷理”?故他在2007年重新回归理雅各的翻译。此外贾氏对仁、新民、中庸等的翻译与理雅各亦有不同,然其高下则各有千秋。
贾氏译文亦有可商处,如他对何晏、朱熹的“克己”有不同翻译,何:to restrain the self;朱:to subdue the selfo① 何晏引马融说把克己解为约束自身,朱熹则解为战胜身之私欲。其语义有两处差别:“克”是约束还是征服? “己”是身体还是作为身体中不好的部分(私欲)?贾氏注意到前者之别,但却将两个意义不同的“己”都译为“self”,显然未达到区别的效果(就笔者寡见所及,英译本少有注意此点者)。即便在朱熹本人的诠释中,此克己之己与本章下句“为仁由己”之“己”亦是意义有别的。
贾氏认为朱熹诠释具有语篇连贯和互文性特点,故对其《四书》的翻译诠释亦采取了整体比照和局部探微相融合的方式。他对具体文本的翻译,总是结合其他相应文本来阐明之。在翻译每条《朱子语类》正文后,适当以小号字体加以阐发,并另外加以注释,基本上引朱解朱。如第七卷小学第一条,即引《大学章句序》解释古人小学和大学的问题。对某些重要核心术语如理气等,贾氏不遗余力的旁征博引,此引注法实得朱熹精髓。既然何晏、朱熹对《论语》有着不同注释,那么《论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贾氏认为,《论语》的真正意义就是读者在文本中发现的意义。《论语》滋哺了保留它为神圣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恒久的重新诠释和重新振作的自我认同中反过来滋哺了对《论语》的阅读与理解。故对注释的学习之于经典文本实际意义的理解珍贵无比。
综合来看,贾氏的朱熹《四书》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比较的研究视野。他把握住朱熹《四书》作为晚近儒学的基本教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和谐整体。并利用《四书章句》之外的材料展开比照性研究,明确了各资料之间的主次先后关系,指出《语类》虽然极具参考价值,但还是应最先参考《四书章句》。通过何晏、朱熹《论语》诠释的具体比较,发现中国经典诠释存在历史与哲学两种模式。二是内在问题意识。著者选择由经典诠释入手来研究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对西方忽视中国经典研究的补充。他注意到注释是中国思想家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故在《四书:后期儒家基本教义》中采用集注的研究形式向英语学界阐释自宋以来理解《四书》的典型方式。其次,著者对中国经典的学习载体——朱子《四书》;表达形式——行间注体裁;诠释方式——魏晋的历史性与宋明的哲学性诠释;学习目的——学以成圣等重要问题都有细致阐述。这些论述对西方目前仍缺乏的中国经典思想研究有很强的补白意义。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历史后半期( 1200—1900年)中国人如何研究《四书》文本并吸收其中的价值观,这在西方极少有研究。另一方面,著者的研究涉及理学经典化、经典诠释义理化、经典宗旨伦理化等重要经学思想论题,对当前日益活跃的经学思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如贾氏认为,朱熹《四书》诠释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理、气、心、性构成的一套形上语言和儒家正统结合起来,提供了更加人类中心主 义的关切。三是采用了以传统经典注释方式为主,辅之以西方论文的形式,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其著作由长篇前言+翻译+注释+结语的结构构成,翻译注释皆极详尽,如对《大学》全书的翻译包括了《大学章句序》,指出“复其性”来自李翱。对已有注释加以批驳,如批评理雅各将“下民”解释为“inferior people”不妥,应为“ the people below ”not“the inferior people”.①当然,贾氏的从思想史展开研究,对朱熹《四书》诸多内在哲学问题如道统、理气、心性等并未给予深入阐发,此是其限制所在。
附注
①《四库全书存目》子部第四册,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789页。
②同上。
③《语类》卷117,第3676页。
①《四库总目提要》言《性理字训》:“大旨亦与淳同。然书颇浅陋……今惟录淳此书,而端之书则姑附存其目焉。”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
②《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
①《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
②《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
③《〈四书集注〉简论》,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页。
④《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⑤《朱子门人与朱子学》,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
①唐君毅《哲学概论》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②《北溪字义》,第21页。
③《定宇集》,四库全书12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④《北溪字义》,第41页。
⑤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①《北溪字义》,第32页。
②《北溪字义》,第41页。
③同上书,第24页。
①《北溪字义》,第6页。
①《读书分年日程》,《四库全书》第70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页。
②“比之程正思、陈安卿为详略适中,而立义措辞尤精。”《续修四库全书》13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③《石堂先生遗集》,第414页。
①《石堂先生遗集》,第408页。
②同上书,第422页。
①《石堂先生遗集》,第422页。
②同上书,第426页。
③同上书,第392页。
①《西山读书记》,《四库全书》第70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34页。
②《定宇集》,第241页。
①《四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②《四书通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35页。
①《书何安子四书后》,程钜夫《雪楼集》卷24,《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9页。
①《勉斋文集·语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09页。
②赵顺孙:《四书纂疏》,第683页。
①《四书集注》,第22页。
②《勉斋文集》,第707页。
③《四书集注》,第23页。
④同上书,第32页。
⑤《勉斋文集》,第802页。
①赵顺孙:《四书纂疏》,第742页。
②《四书集注》,第32页。
①历来有学者持《中庸》两篇说,作为勉斋学重要分支的北山学派的王柏即为二篇说代表,他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将《中庸》分为诚、明两篇。今人亦有持两篇说者。
②《勉斋文集》,第810页。
①《勉斋文集》,第548页。
②同上。
①《勉斋文集》,第548页。
①《勉斋文集》,第548—549页
②《勉斋文集》,第549页。
①《勉斋文集》,第549页。
②《勉斋文集》,第549页。
①《勉斋文集》,第374—375页。
①《勉斋文集》,第375页。
②同上书,第548页。
③《勉斋文集》,第583—584页。
①《勉斋文集》,第584页。
①《勉斋文集》,第462页。
②同上书,第792页。
③同上书,第796页。
①《勉斋文集》,第464—465页。
①可参拙稿《再论饶鲁的<中庸〉章句学及其对朱子的超越》,《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②双峰说获得后世学界的主流认同,如对明代《四书大全》和韩国理学影响甚大的胡云峰《四书通》即采用其说,清末翟灏《四书考异》亦提到双峰与草庐的《中庸》分章,但却极少有人提及勉斋说。
①饶鲁之说几为元以来各主要四书类著作所引述,本文选自清王朝璩辑《饶双峰讲义》卷9,乾隆五十六年石洞书院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贰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草庐之说,见其所著《中庸纲领》,《四库全书》,第12—14页。
①史伯璿:《四书管窥》卷8,第945页。
②对双峰《中庸》思想的详细论述,可参拙稿《饶鲁〈中庸〉学的道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哲学动态》2013年第10期;《饶鲁<中庸>学的工夫论诠释及对朱子的突破》,《山东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③方旭东《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①近来,中外两名学者各撰有综述近年英语学界朱子研究的文章:[美]司马黛兰(Deborah Sorn-mer) : Recent western studies of Zhu xi,载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彭国翔:《近三十年(1980—2010)英语世界的朱子研究:概况、趋势及意义》,《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 Chu Hsi and the Ta-hsueh: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Cambridge and Lon-d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0.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3. The Four Books: the Basic Teachings of the Later Confucian traditio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 Cambridge, 2006。他于 2014年出版的 Confuci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Press)也有专章论述朱熹。
①G. Daniel, Chu Hsi and the Ta - hsueh: Neo -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introduction, p. 3.
②Ibid., p.48.
③Ibid., p.49.
①G.Daniel, Chu Hsi and the Ta-hsueh: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6, introduction, p.63.
②Ibid., p.1.
③G.Daniel, Chu Hsi and the Ta-hsueh: Neo-Confucian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p.7.
①G.Daniel,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 36.
②Ibid. , p. 105
①G. Daniel,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 166.
②Ibid. , p. 169.
③Ibid. , pp. 3-4.
① G. Daniel, Chu Hsi and the Ta - hsueh: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p. 47.
①G. Daniel, Learning To Be a S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Arranged Topical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75.
②G. Daniel, Zhu X’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 32.
①G. Daniel, The Four Books: the Basic Teachings of the Later Confucian Traditio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 139.
②Ibid. , p. 147.
①《近三十年(1980—2010)英语世界的朱子研究:概况、趋势及意义》一文据贾氏所著《朱熹与〈大学〉》、《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使用“Canon”一词来证明其研究的宗教性趋势不妥。
②Ibid. ,p.147.
③Ibid. ,p.101.
④Ibid. ,p.108.
①G. Daniel,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 78.
① G. Daniel, Chu Hsi and the Ta - hsueh: Neo -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p. 78, 注释6.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