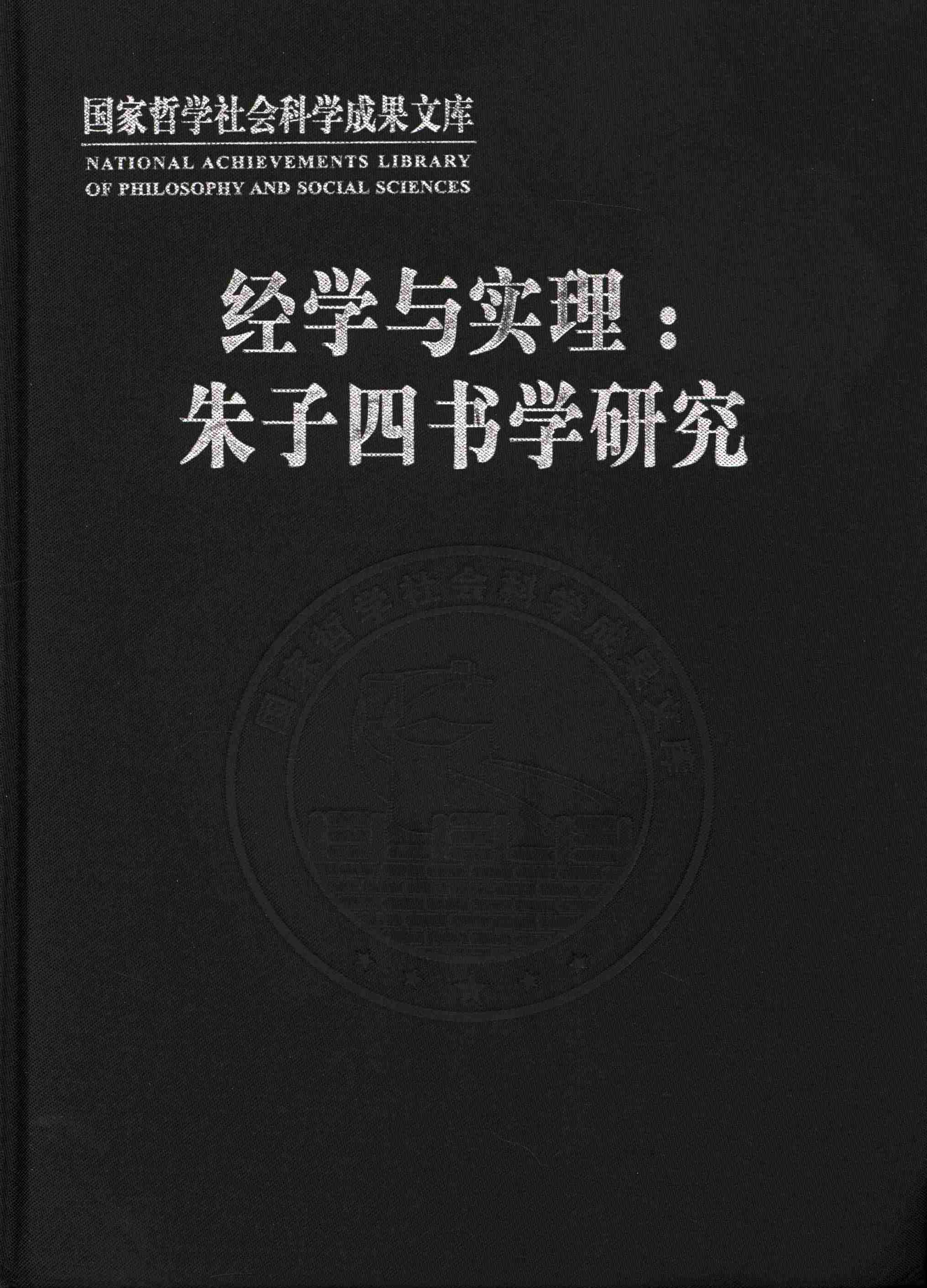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四节 朱子、张栻《癸巳论语说》之辨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42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朱子、张栻《癸巳论语说》之辨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7 |
| 页码: | 386-402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和张栻是理学学者,他们有深厚的学术交谊。在《论语》解释方面,朱熹批评张栻的解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因袭上蔡的错误、解经方法不得当和解释经义时存在偏差。朱熹建议张栻摆脱上蔡的影响,走上新的经典诠释之路。这个案例展示了理学学者相互交往带来的思想演变和理学内部客观存在的思想异同。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学术交谊 |
内容
朱、张深切的学术交谊始终不离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二贤关于《仁说》、《知言》、中和之辩为学界瞩目,然《论语》之辩则似较少受到关注。《论语解》为南轩最费心、晚出、成熟之作,其文本的复杂性,所蕴含的朱张学术异同及理学未来走向问题,实有待发之覆。本书试图以相关证据表明,南轩《论语解》确存在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朱子曾就南轩《癸巳论语说》提出120处修改建议,南轩改本亦多据朱子意见修改而成,体现出朱张思想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四库馆臣囿于所见,得出南轩仅修改《癸巳论语说》23处,其余“拭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等判定不合实际,通行之《南轩论语解》中华版对该书的大量失校亦不利于改本的凸显。另一方面,朱张《论语》之辩体现出二者对理学传统和经典诠释的处理存在守成与创新之异,南轩仍局限于上蔡等理学立场,继续沿袭“六经注我”的求言外之意的高远风格;朱子则遵循以求本意为主的“我注六经”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扬弃理学,融合汉学,实现了经学与理学的合一,将理学之时代精神回归于经学之本始传统,最终开出了儒学发展的新生面。此一个案显示了理学学者相互交往所带来的思想演变、理学内部客观存在的思想异同,朱、张治学理念之异于理学学派兴衰演变之关系等重要论题,于今日儒学发展亦不乏现实参考意义。
一 因袭上蔡之误
朱、张在学习洛学的过程中,皆深受谢上蔡《论语说》影响,上蔡之说可谓二贤早年进入理学之门的“扶手”。但随着朱子学术思想的成熟独立,他开始抛弃这一“扶手”,反思上蔡之不足,通过扬弃上蔡踏上自成一家之路。①南轩则似仍徘徊于上蔡影响之中,故朱子批评南轩《癸巳论语说》多因袭上蔡之误。朱子于《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以下简称《癸巳论语说》)中多次道明此点,如批评父在观其志、所贵乎道者三、曾点之乐等章引上蔡说具有好新奇、缺工夫、远本意、近异端之弊。朱子于《答张敬夫语解》(该书专门答复南轩《论语解》学而篇十章)认为“传不习”当为明道“传而不习”说,南轩通行本则仍持上蔡“传者得之于人,习者得之于我”说。指出“父在观其志”章“不暇改”说是承袭上蔡之误。从文义与工夫的两角度据明道、尹氏说批“所贵乎道者”章因袭上蔡之误,“此说盖出于谢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义理观之,则尤有病……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而其效验乃见于此,意味尤觉深长。明道、尹氏说盖如此,惟谢氏之说以‘动’、‘正’、‘出’为下功处,而此解宗之……且其用力至浅而责效过深,正恐未免于浮躁浅迫之病,非圣贤之本指也”②。认为南轩采用谢氏说不合夫子意,用力太浅而言效过快过深,易造成浮躁急迫学风。南轩接受之,通行本删“将死而言”句,采朱子“庄敬笃实,涵养有素”说,并反思上蔡说的确缺少下工夫处而转向二程说。《答朱元晦》言,“‘所贵乎道者三’,上蔡之说诚欠却本来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①。朱子于曾点之乐章严厉批评上蔡说杂入佛道而无圣贤气象,指出南轩说即源于此。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曽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著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其说。②
批评南轩说过于花哨虚浮而无扎实深沉之味,文意相互矛盾太多。如“曽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句有双重错误:一则文义有误。“非有乐”是明道对颜子箪瓢之乐的评论,不可施于曾点。颜、曾之乐不同,颜乐在箪瓢陋巷之外,不可即其事而求;曾乐是见道分明,洒脱无累之乐,正当即其事而求。二则宗旨有误。以此浮夸之言解曾点,使夫子师徒问答,陷入禅宗拈槌竖拂之机锋,几乎推圣门于禅学。此体现了朱子严辨儒佛的学术立场。指出南轩摆落圣言直抒己见,过于自信而轻视圣贤,立说过高归于空虚,并以其表意混乱的“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不及”等说证明之。批评上蔡仅赞叹曾点无牵挂洒脱意而未发明仁者爱物之心,引《列子》为解更杂入老庄之见而无圣贤气象。归结南轩之误为受上蔡影响故,告诫南轩当摆脱上蔡说不良影响,走上新的经典诠释之路。通行本接受朱子意见,删除被批评诸说。《集编》、《读书记》所引较通行本又有精简。
二 解经三宗病
朱子于癸巳前后反思理学直阐己意的解经之弊,强调当汲取汉代训诂章句学之优长,以救其弊。《答张敬夫》多封书信皆反复明确此意,如癸巳《再答敬夫论中庸章句》强调章句分析之学与玄谈心性之学的区别。癸巳《中庸集解序》严厉批评脱略章句之空的后果更胜于汉人章句之陋,表明力图扭转空谈之学,回归章句文本,沉潜文义解读,探寻文本原意,追求平实简易的主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①为此,朱子特别反思予其以深刻影响的上蔡论语学,批评上蔡解经存在虚浮不实、新奇不平;缺少工夫指点;杂佛老以解儒典的毛病。认为此即南轩所染之病,故对《癸巳说》的批评,皆围绕此三方面展开。
(一)“贪说高远”
朱子解经反对好高凿深之论,力求平实、浅易、贴切。对南轩高远之说,以“不(未)安”评之,甚不喜南轩套用“性”“天理”等形上概念解经,指出此是造成其解高远的重要原因。如认为南轩“众人物其性”说“此语未安,盖性非人所能物”。②批评其“形体且不可伤,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的“伤性”说过高,既不合曾子本意,亦不合事理,本意只是保全形体,通行本未改。批评其“约我以礼,谓使之宅至理于隐微之际”说“幽深,却无意味”,乃是受谢氏影响而未免好高之弊。《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南轩“明尽天理”说亦犯有高远之弊,“‘患不知人’恐未合说到明尽天理处,正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虽比旧说已为平稳,尚时有贪说高远,恐怕低了之意”③。南轩接受之,删除“明尽天理”并提出反对贪高务远说。
南轩喜用夸张性表述,立说过高而不妥当、平实,易造成逻辑混乱。《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其以“美玉之与碔砆”喻夫子乐而好礼、子贡无谄无骄不妥,此喻只能用于王霸之别等性质对立者,通行本改之。朱子又指出南轩以“言当其可,非养之有素不能”解“三愆”过高,圣人只是戒人言语以时,不可妄发之意。通行本未改。评析南轩贪图高远的说经风格还见诸以外在目的、关系解经,如“以成性、以养德”等说。批评禹吾无间然矣章“所以成性”说不妥,大禹所为皆是理所当为,非为成就性而为之。批评“艺以养德”说,认为艺是事理不可或缺之当然,是合有之物,游于艺并非把“艺”作为一外在于德性的手段。直指南轩解源于不屑平实,好为高远的解经大病。“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此解之云,亦原于不屑卑近之意,故耻于游艺而为此说以自广耳。”①批评南轩“言欲讷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职”说、“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亏其所以生者,则其生也亦何为哉”说,皆有计较功利之意。进一步剖析南轩贪说高远的风格源于其“几欲与《论语》竞矣”的心态,批评其奢则不孙章“圣人斯言,非勉学者为俭而已”说即犯有此病,“今为此说,是又欲求高于圣人而不知其言之过,心之病也。……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②。无友不如己章南轩提出“不但取其如已者,又当友其胜已者。”朱子指出只是“友必胜已之意”,批评南轩分此为二等是欲高出圣人之言,此为其解经之普遍毛病。“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③反之,朱子亦批评南轩犯有过于推崇圣人的倾向,“尊圣人之心太过”。如放郑声章指出其“于此设戒是乃圣人之道”说不合文意,推崇圣人过度,反致气象轻浮狭隘。通行本未改。
(二)“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
朱子不满摆落本意、一味阐发己说的解经做法,主张解经当以阐发本文之意为宗旨。其对南轩的批评亦针对于此。批评南轩述而不作章“圣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仅以“平易”为解,未能阐发圣人谦虚诚实之意,未使学者识圣人气象,消虚傲之习。批评其以“老彭孔子事同而性情功用异”比较圣人与老彭,与经文之意大背,反陷圣人之谦虚诚实于虚伪之境。总结其病在于多发明言外之意而反背离本文宗旨。“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①通行本已删此二句。批评南轩“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独可行三军而巳”说,认为此恰是针对三军而发,南轩说有过于推演言外意义之弊。批评子帅以正章“明法勑罚以示之,亦所以教也”说虽合事理却“夺却本文正意”。朱子常指出南轩解不合经文之意,乃外来无据之说,“经文未有此意”。如指出谅阴章“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说“经文未有此意”“无来历也。”批评原壤章幼而孙弟说“恐圣人无此意”;指出予一以贯之章“此亦子贡初年事”说无据,非经之本意。以上通行本皆未改。朱子亦指出南轩说常偏离主旨而无当。如批评南轩“无其鬼神是徒为谄而巳”说偏离章旨;修己以敬章“敬有浅深一句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主张删除“敬有浅深”及“亦”字。与此相应,朱子还提出阙疑的审慎态度。如提出谨量章“此篇多阙文,当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阙之可也”②。
(三)“圣人与异端不同处不可不察”
朱子对南轩的批评,特别注重严辨儒学与佛老之别,严格甄别佛老用语、思想的掺入。如反对子谓颜渊章“其用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的“无意”说,而主张无私意,以区别儒学与佛老异端之学。“谓舍之而犹无意于藏,则亦过矣。……圣人与异端不同处,正在于此,不可不察也。”③通行本未改。仲尼焉学章南轩采用龟山等“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莫非文武之道,初无存亡增损”说,朱子批评此说因新奇而为学者所多用,然不合文义。“盈于天地之间”与“文武之道”“无存亡增损”自相矛盾。文武之道只是指周朝制度典章,批评迁儒说以就佛老之言,丧失儒家下学之义,陷入异端目击心会之说,要求南轩平心退步,反复探究句读文义而明此说之失。“近年说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万物盈于天地之间’,则其为道也,非文武所能专矣。……且若如此,则天地之间,可以目击而心会……窃详文意所谓文武之道,但谓周家之制度典章尔。……大抵近世学者喜闻佛老之言,常迁吾说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读者平心退步,反复于句读文义之间,则有以知其失矣。”①庚寅《答张敬夫》批评南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说未能严辨儒道之别,“大凡老子之言与圣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②朱子甚留意于具体字义中辨别儒佛。如南轩解语之而不惰为“不惰其言”,朱子则主张为“怠惰”,认为如南轩说,当为“堕”字,且有禅学“语堕”之意,极不可取,批评上蔡等以“不惰为领受”错误。
三文义章句之辨
朱子在注释《四书》的过程中,逐渐从一味阐发己意的理学学风中走出,而兼采重文义解释的训诂章句之学。强调从文义入手,准确、平实解读经文,以扫除阅读障碍,疏解文本之义为宗旨,融合了理学之义理精神与汉学之小学传统,重铸了经学之解释形态。朱子对此转变有深刻反思,再三强调回归汉儒以训诂解经的经训合一之学,如此方能力求本旨而意味深长。《答张敬夫》言:“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③丙申《答敬夫孟子说疑义》明确了由字义到文义再到本来意的解经次第,突出解释文义名物为解经之首务,反对过多阐发己意,而主张简易。“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④故朱子据详辨文义章句的宗旨,从文字、用语、句法三个层面指出南轩《癸巳论语说》的不足。
(一)文字之形音义
字、音之误。朱子指出南轩两次引文之误,一为误引伊川“思绎”为“䌷绎”。“本文作‘思绎’,今此所引改‘思’为‘䌷’。”⑤然通行本未改。二是指出“抑”字之误,“知抑精矣”,通行本改为“则益精矣。”对字音的理解决定了字义把握和义理领会,朱子《四书》于注音用心非常之细,尤关注多音多义字。如“恶”字,南轩曾读“苟志于仁无恶也”的“恶”为去声,可恶义,朱子提出当为入声,乃不善义。“盖此章恶字只是入声。”①又如南轩解默而识之为“黙识非言意之所可及,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世之言黙识者,类皆想象意度,惊怪恍惚”。朱子指出“黙识只是不假论辨而晓此亊理”,批评南轩解已流入自身所批评的“惊怪恍惚”之列,其因在于对“识”的读音有误。《集注》更倾向“识”的“志音,记义”。“不施其亲”的“施”,南轩主张尹氏说,朱子则取《经典释文》和吕氏说,认为当是“弛”字,批评谢氏释为“施报”有误。“若如谢氏,虽亦引‘无失其亲’为解,然却训‘施’为‘施报’之‘施’,则误矣。……《释文》本作‘弛’字,音诗纸反…今当从此音读。”②
字义辨析。朱子极重视字义辨析,于此批评南轩说之不足。如“罔之生”的“罔”,南轩主蒙昧义,“罔则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近于范氏“无知”说,朱子据上文主张为伊川“欺骗”说。批评南轩子绝四章的“绝而不复萌”说,认为“绝”当是“无”。言绝不言无,更显出无之程度深。南轩采纳之。朱子常以古注取代诸家说。如“人也”南轩解为“以其有人之道也”,此来自范氏“尽人道”说,朱子认为当是古注“伊人”说,南轩改从朱子。朱子判定字义诠释的标准是自然简易。如不可则止的“止”,南轩主“制止”义,朱子认为是离开义,批评其解穿凿费力。“按经文意,‘不可则止’但谓不合则去耳。……今为此说穿凿费力而不成文理。”③朱子对语气词等虚词颇用心,如不逆诈章南轩认可孔安国“先觉人情者,是宁能为贤乎”解,朱子则强烈反对,称赞杨氏说,指出“抑”为反语之词,表推测、可能关系。
“字未安”“不可晓”。朱子常以“字未(不)安”的形式指出南轩用语不妥。如南轩解敬鬼神而远之为“远而不敬,是诬而已”。朱子指出“诬字未安”,通行本改为“忽”。但朱子所批评者,南轩多未改。如“处于己者不尽也”的“处字未安”;“语乱则损志”的“损志二字未安”;“不忍乘危”的“乘危二字未安”;“包注训固为陋”说“恐亦未安”;“信于己也”的“己字未安”等。朱子批评南轩子之燕居章“圣人声气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随形”说,以形影关系阐发圣人声色之不离,并不贴切,反而有化二为一的嫌疑,未能揭示圣人与常人之别,圣之为圣所在。朱子亦批评南轩用语“不可晓”。或因太简略之故,如认为“将死而言善,人之性则然”说,“此语太略,几不可晓,恐当加详焉”①。或为表述不清而难以理解。如“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圣人所欲不存岂有一毫加于此哉”,皆认为“不可晓”。
(二)“自相矛盾”“未尽曲折”及“设问发之”
朱子指出南轩说存在前后文意自相矛盾处。如“质胜文则野”章南轩先言“与其史也宁野”,再言“矫揉就中”“修勉而进其文”,文理错杂,前后矛盾,使学者不知用力之方。“与其史也宁野”是无法做到中之后求其次,南轩则先此而后再“就中”。通行本接受批评,采取了删“矫揉就中”等做法。朱子以“语序颠倒”指出南轩说语义矛盾,如批评“仁者为能克己”颠倒了克己与仁的由工夫而本体关系。指出南轩说具有过于牵扯,“说过两节”“跨过两章”的弊病。如自行束修章先后引夫子“何莫非诲”“不保其往”说,朱子认为“此一章之中而说过两节意思,尤觉气迫而味短也”。②中人以上章引孟子“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于文意、气象皆不合,为南轩采纳。
朱子指出南轩说有“未尽曲折”“不亲切”“太支离”的弊病。如批评信近于义章“此结句似不分明,恐未尽所欲言之曲折也”③,指出“夫子听卫国之政,必自卫君之身始”说虽合理,却少曲折。批评直躬章“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实者”说“此不知所指言者谓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④,指出如患得之章“计利自便之心”说文义不分明、语意亦不亲切。通行本未改,《集编》《读书记》所引改为“患无以得之也”。批评士见危致命章引龟山说“于成人曰授命、曰见利;于士曰致命、曰见得”太支离,通行本未改。朱子亦批评南轩解无关主旨,如生而知之章“其至虽一,而其气象规模终有不同者”是多余不必要之说。
朱子在认可南轩解的同时,亦提出其需改进“发之无端”的突兀表达,建议采用“先设疑问以发之”的或问体,以实现表意自然、顺畅;明确言外之意与本文正意的区别,避免掺杂。朱子曾数次告之当采用“或问”体。如南轩以隐显、内外、本末解“一以贯之”章,朱子认为解意虽善而立言无端,导致杂乱无序,当采设问方式。指出南轩巧言令色解内容甚好,只是为言外之意,应有所引语方不显突兀,避免与经文正意的混杂,做到义理分明,并以伊川《易传》必设问以发言外义为证。“此意甚善,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此语方有所指。……如《易传》中发明经外之意,亦必设为问答以起之,盖须如此方有节次来历,且不与上文解经正意相杂。”①南轩接受之,通行本补“其心如之何”之设问句。朱子针对就有道而正焉章、克己复礼章提出同样建议,前者未改,后者采纳。
四 《论语解》改本及朱张异同
(一)《论语解》之癸巳本与淳熙本
朱子对南轩《癸巳论语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辨析,南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朱子意见,对该书加以修改,形成了与癸巳旧本差别较大的淳熙改本。②淳熙年间,南轩反复提及对《论语说》的改正,朱子、吕祖谦亦皆认可淳熙改本大优于癸巳旧本。南轩《答朱元晦》言:“《语说》荐荷指谕,极为开警。近又删改一过,续写去求教。”③朱子《张南轩文集序》言:“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晚尝更定,今已别行。”④《答吕伯恭》言:“詹体仁寄得新刻钦夫《论语》来,比旧本甚不干事。”①吕祖谦答《朱侍讲》亦言,“詹体仁近亦送葵轩《论语》来,比癸巳本益复稳密”②。
朱子《答张敬夫语解》、《癸巳论语说》引用约130条南轩《论语说》,并指出其应修改之处,如将之与通行本相较,则会认同四库馆臣仅修改23处说;如将之与《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所引南轩说相对照,即可发现半数以上实已修改。所改之处多据朱子批评,此即为淳熙改本说。真德秀《四书集编》在“子谓颜渊章”明确提出淳熙本与初本的差别。“南轩初本云:‘其行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③且详引朱子《癸巳说》批语。可见他同时见过初本与定本,且非常注意二者区别。《四书集编》引南轩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辨析朱、张异同,如不以二家定本为据,则辨析将无从展开。如多见而识,《集注》解为“识,记也。记则善恶皆当存之。”南轩为“多见而识其善”。德秀认为:“多见而识之一句,二先生所释不同,以文义求之,则南轩似优。”④“不至于谷”,朱子释“谷”为“禄”、南轩为“善”,德秀又指出,“二先生释谷之义不同,正宜参玩”⑤。至于《集注》、《或问》所引南轩说,几乎皆为朱子所赞同者,而朱子对南轩初说则多有不满,故二书所引当为改本说。此外,今本保留了二十五条作为异文的“一本”“一作”说,此“一本(作)”说除少数一、二条外,亦大体同于《集编》等所引,可知基本为淳熙修订说。遗憾的是,今中华版虽已采《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加以校勘,但仅校出约30处,据笔者考察,当有约190处。
(二)《论语解》之具体修订
四库馆臣认为南轩仅接受朱子《癸巳论语说》之23条批评,由此判定朱、张之学诚可谓“龂龂不合”,归其因为讲学家辨难习气,求胜心切使然。当“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之后,则不复相争,“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彼此“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朱、张最终“不改不争”本应显示彼此之异,馆臣反而得出“终同”的结论,盖其认为朱子癸巳对南轩之异议后皆改之,故不争,不可以朱子癸巳之见来否定南轩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①其义明显指向朱子批评之说并不可靠,是朱子改变己说而非南轩。笔者结合《集编》、《读书记》等资料,立足南轩淳熙改本,认为这一判定明显颠倒事实。南轩通行本接受、修改《癸巳说》者约为61条,而非23条。包括通行本改之、《集编》(并《读书记》、“一作”等)改之、仅《读书记》改之、仅“一作”改之等情况。且大体遵朱子意改。其中通行本所改22条;“一本”“一作”所改5条;《集编》、《读书记》引所改23条;“一作”、《集编》引改“古之学者为己”章1条;《读书记》引改“三愆”章2条;通行本略改,《集编》引大改8条。另有一半未修改者,有以下可能:南轩坚持己见未改;朱子改变看法;朱子批评本来无关紧要;南轩已改而今本未见。朱子癸巳《答张敬夫论语解》专就南轩《论语说》学而篇10章提出批评,对比《癸巳论语说》、通行本《论语解》、《四书集编》所引可知,南轩大部分据朱子意见改之。学而、巧言令色、三省章《癸巳论语说》已改之;父在观其志、信近于义、贫而无谄、不己知章通行本改之;友不如己章《集编》引改之。道千乗之国章未改,源于朱子自身思想改变。慎终追远章未改。据本人研究可知②,《集编》等所引南轩《论语》说较通行本实修改172章,诸多内容明显遵朱子之意修改,修改的共同特征是以精简为本,删繁就简,几乎每章皆有删除。修改之说在思想上与《集注》更接近,手法上更重视文义解释,风格上趋于平实,文字上更简约、精炼。综上可知,南轩淳熙本《论语解》受朱子影响很深,学术立场和观念有很大转变。进而最终认同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反思上蔡不足。《答朱元晦》言:“上蔡《语解》偏处甚多,大有害事处。”③
(三)朱张早晚异同论
南轩《论语说》受朱子影响颇深,但朱子同样受到南轩影响。二者思想异同情况颇为复杂,大体有始异终同、始同终异、始终皆同、始终皆异四种情况。“始异终同”,即朱子初批南轩而终同其说,此是朱子前后自我否定、认识逐渐加深之故。四库馆臣以三年无改章为例,指出朱子否定南轩《癸巳论语说》解,但《论语集注》采孔安国义,则与南轩说同。朱子曾认同“道千乘之国”的“道”解为“导”,《答張敬夫语解》反对南轩“治”解,后转而认可南轩解。颜渊季路侍章朱子对南轩“施”为夸张,“劳”为功劳的新说表示怀疑,倾向于施加、劳事之旧说。《集注》则以“夸大功劳”之说为第一说,保留旧说为二说,更认同南轩说。“始同终异”,即朱子早年同于(未反对)南轩说,后来则反对之。此类情况甚多,恰见出朱子思想之转进与创新。典型者如知仁动静,朱子曾以南轩仁知动静说为周子《太极图说》之意,认为“此义甚精,盖周子太极之遗意,亦已写入《集注》诸说之后矣”①。但今《集注》并无南轩说,且所论与南轩说恰相对。又如“因不失其亲”,南轩本二程说紧扣礼义而论,认为“若夫安于礼义,则此又不足以言之矣。”朱子批评南轩貌恭、言信说,但受二程、延平等影响,亦把“因不失”置于“礼义”基础上。《集注》则认为本章主旨是言行谨始而非礼义。此显出朱子说的阶段性和变易性,反映了朱子挣脱前人,独立门户之艰难。“始终皆同”,即朱子始终大体认可南轩说。《论语集注》收入南轩说8处,《四书或问》引用33处,赞赏其说“可取”、“亦佳”、“可观”等(仅“有教无类”章认为其说有得有失)。此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同时收入《集注》《或问》的三章:使民敬忠以劝、闻斯行诸、佛肸召章,此三章《癸巳论语说》亦无异议。另《或问》未提及而《集注》收入5章,表明朱子当在丁酉《或问》之后才认可南轩此说,可视为始异终同。“始终皆异”,即朱子、南轩各自坚持己见而不求苟同,如上述朱子所批评之《癸巳论语说》,通行本尚有约60条未改者,可暂视为此类。此充分体现了二者之学的特色与差异。
朱张的差异还见诸对洛学诸家的取舍上,南轩于《精义》诸家尤其是上蔡、龟山说守成较多,在诠释方法上亦是继承理学阐说大意,不屑卑近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张栻宗奉二程而罕有批评。朱子亦同样宗奉二程,但朱子此时对南轩的批评多指向上蔡而罕及二程,在此后的丁酉《或问》和己酉《集注》阶段,则对二程多有批评。盖伴随着学术方法的自觉与学术思想的自信,朱子对洛学的批判态度逐步加深,最终从义理和解释方法上超越理学,回归经学。此一一味“宗程”与适度“非程”之别,根源于朱、张在经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如将南轩《论语解》与朱子《论语集注》稍一比较,二者之别即历历在目。如《论语》首章南轩认为朋来之乐的原因是“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资已,讲习相滋,其乐孰尚”。此乃综合伊川、龟山说,《集注》则取伊川而批龟山。南轩解“不愠”为“盖为仁在已,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看似同于《集注》所引尹氏说,然朱子反对以“仁”解“学”,盖易致好高、好空、好悟的弊病。在解释方法上,朱子特别指出南轩忽视“字义”,如“学而时习之”五字,每字皆有意味,应逐字详说而不可简略。学者指出其因在于南轩之学实浸染于以二程为代表的时风习俗之中。①此外,朱子与南轩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南轩对朱子说之接受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怀,其对朱子说的拒绝和有保留地部分认可,亦见出南轩始终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虽因朱子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
(四)改本之意义
南轩《论语解》淳熙改本是在吸收朱子建议基础上,朝着精简、平实、注重文义、贴切文本的方向修改而成。是否认识到南轩《论语解》存在前后改本,直接影响对南轩思想及朱、张学术关系,甚至理学思潮演变的理解。学界对南轩《论语》思想的论述颇精,然似忽视了南轩《论语》思想前后的差别,而仅以癸巳本与通行本《论语解》立论,导致所论未尽乎善。如有学者据“博施于民”章“仁道难名,惟公近之”说论证张栻承袭明道“以公言仁”说①,而据《集编》所引、一本云,此说早已不见于淳熙改本,改本突出了仁者之心,仁者之方,其结语亦由通行本的赞颂态度(“先言仁者而后以仁之方结之,圣人之示人至矣”)转为批判语气(“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则知以博施济众言仁者,其亦泛而无统矣”)。也有学者认为,南轩《论语解》宗奉二程,大量引二程之学,举学而章引程子“时复䌷绎”说为例,淳熙本已删此说,改为“重复温绎”;据“为己为人”章“学以成已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说,指出其解合于二程,其实在朱子批评南轩以成物解成人说不妥的影响下,作为改本之说的“一本云”已删除“所谓成物”句。学者还指出“张栻《论语解》全书直接引述二程之说共32处”,此处“《论语解》”前当补“旧本”二字方确。②
五 创新与守成
朱子与南轩的学术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如中人以上章,南轩有“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南轩采用孟子“是亦所以教之”说解本章,于文意及气象皆不合。孟子不屑之教是绝之而不再教诲,本章夫子提出施教,要求就学者地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切实的教育之方,并非弃绝不教。南轩此说,有凡来学者皆告以性与天道之极之意,否则绝而不教。朱子措辞极为激烈地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而且就文本言,亦造成文意躐等断绝,气象不佳。故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其“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乃所以渐而进之,使其切问近思而自得之也”为南轩完全采纳。南轩对朱子说之接收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虚胸怀,然其对朱子说的拒绝,亦证明南轩始终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之理学家,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上所述,南轩对朱子的批评常有坚持未改者,即便接受,亦表现为有保留的部分认可而非全盘接受。如君子有恶章,朱子认为“夫子之问,未见恶人之疑;子贡之对,亦未见检身之意”。①今解已不见“恶人之疑”,而有“所以检身”说。有时尽管朱子再三苦口,南轩仍坚守己见,不为所动(当然,此仅就现存文献而论)。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论语解》为“如自孝弟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其爱虽有差等,而其心无不溥矣。”《癸巳说》采用了朱子“故孝弟立,则仁之道生”说,因朱子之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言“本立则其道生而不穷”。《集注》则解到“生”字为止,认为“无穷”字高远而不切意。本章讨论了“由孝弟可以至于仁否?”《集注》取伊川说,阐明仁与孝悌为体用、性情关系,南轩则简略认为视孝悌与仁为不同事物者失其宗旨。
朱子据其对经典诠释的新理解,主张吸收汉代章句训诂之学的长处,以纠正理学忽视文本字义之弊,而集矢于南轩《癸巳论语说》及上蔡说。南轩对朱子思想有所认同吸收,淳熙改本据其所论多有修改。在《论语》之辩中,南轩受朱子影响较大,故朱子屡称赞南轩的最大优点是闻善即迁。“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论语》旧说,某与议论修来,多是此类。”②此昭示我们应在尽量把握南轩《论语》前后改本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前后演变有整体性和连续性认识,而免于陷入对研究对象的平面化、断裂性理解。朱、张虽同宗二程而实则程度、态度有别,钱穆先生早已指出朱、张之异:“盖当时理学界风气,读书只贵通大义,乃继起立新说。……即南轩亦仍在此风气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③此为中肯之论。它提醒我们在肯认程朱理学作为一整体学派的同一性之时,亦应对其内部的差异性有所分疏。南轩在与朱子的反复交流中虽有所改变,然总体仍因袭二程理学之诠释范式。朱子则直面理学解经之弊,融合汉学、宋学解经之长,寓创新于守成之中,融经学与理学为一体,树立起新的经典典范,推动了理学的向前发展。朱、张在解经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守成之异,近则作用于湖湘学与朱子学彼此之衰退兴盛,远则关乎理学与经学之未来演变。其于今日儒学之继承与创新,亦不无启示意义。
一 因袭上蔡之误
朱、张在学习洛学的过程中,皆深受谢上蔡《论语说》影响,上蔡之说可谓二贤早年进入理学之门的“扶手”。但随着朱子学术思想的成熟独立,他开始抛弃这一“扶手”,反思上蔡之不足,通过扬弃上蔡踏上自成一家之路。①南轩则似仍徘徊于上蔡影响之中,故朱子批评南轩《癸巳论语说》多因袭上蔡之误。朱子于《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以下简称《癸巳论语说》)中多次道明此点,如批评父在观其志、所贵乎道者三、曾点之乐等章引上蔡说具有好新奇、缺工夫、远本意、近异端之弊。朱子于《答张敬夫语解》(该书专门答复南轩《论语解》学而篇十章)认为“传不习”当为明道“传而不习”说,南轩通行本则仍持上蔡“传者得之于人,习者得之于我”说。指出“父在观其志”章“不暇改”说是承袭上蔡之误。从文义与工夫的两角度据明道、尹氏说批“所贵乎道者”章因袭上蔡之误,“此说盖出于谢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义理观之,则尤有病……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而其效验乃见于此,意味尤觉深长。明道、尹氏说盖如此,惟谢氏之说以‘动’、‘正’、‘出’为下功处,而此解宗之……且其用力至浅而责效过深,正恐未免于浮躁浅迫之病,非圣贤之本指也”②。认为南轩采用谢氏说不合夫子意,用力太浅而言效过快过深,易造成浮躁急迫学风。南轩接受之,通行本删“将死而言”句,采朱子“庄敬笃实,涵养有素”说,并反思上蔡说的确缺少下工夫处而转向二程说。《答朱元晦》言,“‘所贵乎道者三’,上蔡之说诚欠却本来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①。朱子于曾点之乐章严厉批评上蔡说杂入佛道而无圣贤气象,指出南轩说即源于此。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曽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著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其说。②
批评南轩说过于花哨虚浮而无扎实深沉之味,文意相互矛盾太多。如“曽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句有双重错误:一则文义有误。“非有乐”是明道对颜子箪瓢之乐的评论,不可施于曾点。颜、曾之乐不同,颜乐在箪瓢陋巷之外,不可即其事而求;曾乐是见道分明,洒脱无累之乐,正当即其事而求。二则宗旨有误。以此浮夸之言解曾点,使夫子师徒问答,陷入禅宗拈槌竖拂之机锋,几乎推圣门于禅学。此体现了朱子严辨儒佛的学术立场。指出南轩摆落圣言直抒己见,过于自信而轻视圣贤,立说过高归于空虚,并以其表意混乱的“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不及”等说证明之。批评上蔡仅赞叹曾点无牵挂洒脱意而未发明仁者爱物之心,引《列子》为解更杂入老庄之见而无圣贤气象。归结南轩之误为受上蔡影响故,告诫南轩当摆脱上蔡说不良影响,走上新的经典诠释之路。通行本接受朱子意见,删除被批评诸说。《集编》、《读书记》所引较通行本又有精简。
二 解经三宗病
朱子于癸巳前后反思理学直阐己意的解经之弊,强调当汲取汉代训诂章句学之优长,以救其弊。《答张敬夫》多封书信皆反复明确此意,如癸巳《再答敬夫论中庸章句》强调章句分析之学与玄谈心性之学的区别。癸巳《中庸集解序》严厉批评脱略章句之空的后果更胜于汉人章句之陋,表明力图扭转空谈之学,回归章句文本,沉潜文义解读,探寻文本原意,追求平实简易的主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①为此,朱子特别反思予其以深刻影响的上蔡论语学,批评上蔡解经存在虚浮不实、新奇不平;缺少工夫指点;杂佛老以解儒典的毛病。认为此即南轩所染之病,故对《癸巳说》的批评,皆围绕此三方面展开。
(一)“贪说高远”
朱子解经反对好高凿深之论,力求平实、浅易、贴切。对南轩高远之说,以“不(未)安”评之,甚不喜南轩套用“性”“天理”等形上概念解经,指出此是造成其解高远的重要原因。如认为南轩“众人物其性”说“此语未安,盖性非人所能物”。②批评其“形体且不可伤,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的“伤性”说过高,既不合曾子本意,亦不合事理,本意只是保全形体,通行本未改。批评其“约我以礼,谓使之宅至理于隐微之际”说“幽深,却无意味”,乃是受谢氏影响而未免好高之弊。《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南轩“明尽天理”说亦犯有高远之弊,“‘患不知人’恐未合说到明尽天理处,正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虽比旧说已为平稳,尚时有贪说高远,恐怕低了之意”③。南轩接受之,删除“明尽天理”并提出反对贪高务远说。
南轩喜用夸张性表述,立说过高而不妥当、平实,易造成逻辑混乱。《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其以“美玉之与碔砆”喻夫子乐而好礼、子贡无谄无骄不妥,此喻只能用于王霸之别等性质对立者,通行本改之。朱子又指出南轩以“言当其可,非养之有素不能”解“三愆”过高,圣人只是戒人言语以时,不可妄发之意。通行本未改。评析南轩贪图高远的说经风格还见诸以外在目的、关系解经,如“以成性、以养德”等说。批评禹吾无间然矣章“所以成性”说不妥,大禹所为皆是理所当为,非为成就性而为之。批评“艺以养德”说,认为艺是事理不可或缺之当然,是合有之物,游于艺并非把“艺”作为一外在于德性的手段。直指南轩解源于不屑平实,好为高远的解经大病。“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此解之云,亦原于不屑卑近之意,故耻于游艺而为此说以自广耳。”①批评南轩“言欲讷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职”说、“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亏其所以生者,则其生也亦何为哉”说,皆有计较功利之意。进一步剖析南轩贪说高远的风格源于其“几欲与《论语》竞矣”的心态,批评其奢则不孙章“圣人斯言,非勉学者为俭而已”说即犯有此病,“今为此说,是又欲求高于圣人而不知其言之过,心之病也。……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②。无友不如己章南轩提出“不但取其如已者,又当友其胜已者。”朱子指出只是“友必胜已之意”,批评南轩分此为二等是欲高出圣人之言,此为其解经之普遍毛病。“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③反之,朱子亦批评南轩犯有过于推崇圣人的倾向,“尊圣人之心太过”。如放郑声章指出其“于此设戒是乃圣人之道”说不合文意,推崇圣人过度,反致气象轻浮狭隘。通行本未改。
(二)“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
朱子不满摆落本意、一味阐发己说的解经做法,主张解经当以阐发本文之意为宗旨。其对南轩的批评亦针对于此。批评南轩述而不作章“圣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仅以“平易”为解,未能阐发圣人谦虚诚实之意,未使学者识圣人气象,消虚傲之习。批评其以“老彭孔子事同而性情功用异”比较圣人与老彭,与经文之意大背,反陷圣人之谦虚诚实于虚伪之境。总结其病在于多发明言外之意而反背离本文宗旨。“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①通行本已删此二句。批评南轩“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独可行三军而巳”说,认为此恰是针对三军而发,南轩说有过于推演言外意义之弊。批评子帅以正章“明法勑罚以示之,亦所以教也”说虽合事理却“夺却本文正意”。朱子常指出南轩解不合经文之意,乃外来无据之说,“经文未有此意”。如指出谅阴章“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说“经文未有此意”“无来历也。”批评原壤章幼而孙弟说“恐圣人无此意”;指出予一以贯之章“此亦子贡初年事”说无据,非经之本意。以上通行本皆未改。朱子亦指出南轩说常偏离主旨而无当。如批评南轩“无其鬼神是徒为谄而巳”说偏离章旨;修己以敬章“敬有浅深一句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主张删除“敬有浅深”及“亦”字。与此相应,朱子还提出阙疑的审慎态度。如提出谨量章“此篇多阙文,当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阙之可也”②。
(三)“圣人与异端不同处不可不察”
朱子对南轩的批评,特别注重严辨儒学与佛老之别,严格甄别佛老用语、思想的掺入。如反对子谓颜渊章“其用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的“无意”说,而主张无私意,以区别儒学与佛老异端之学。“谓舍之而犹无意于藏,则亦过矣。……圣人与异端不同处,正在于此,不可不察也。”③通行本未改。仲尼焉学章南轩采用龟山等“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莫非文武之道,初无存亡增损”说,朱子批评此说因新奇而为学者所多用,然不合文义。“盈于天地之间”与“文武之道”“无存亡增损”自相矛盾。文武之道只是指周朝制度典章,批评迁儒说以就佛老之言,丧失儒家下学之义,陷入异端目击心会之说,要求南轩平心退步,反复探究句读文义而明此说之失。“近年说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万物盈于天地之间’,则其为道也,非文武所能专矣。……且若如此,则天地之间,可以目击而心会……窃详文意所谓文武之道,但谓周家之制度典章尔。……大抵近世学者喜闻佛老之言,常迁吾说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读者平心退步,反复于句读文义之间,则有以知其失矣。”①庚寅《答张敬夫》批评南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说未能严辨儒道之别,“大凡老子之言与圣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②朱子甚留意于具体字义中辨别儒佛。如南轩解语之而不惰为“不惰其言”,朱子则主张为“怠惰”,认为如南轩说,当为“堕”字,且有禅学“语堕”之意,极不可取,批评上蔡等以“不惰为领受”错误。
三文义章句之辨
朱子在注释《四书》的过程中,逐渐从一味阐发己意的理学学风中走出,而兼采重文义解释的训诂章句之学。强调从文义入手,准确、平实解读经文,以扫除阅读障碍,疏解文本之义为宗旨,融合了理学之义理精神与汉学之小学传统,重铸了经学之解释形态。朱子对此转变有深刻反思,再三强调回归汉儒以训诂解经的经训合一之学,如此方能力求本旨而意味深长。《答张敬夫》言:“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③丙申《答敬夫孟子说疑义》明确了由字义到文义再到本来意的解经次第,突出解释文义名物为解经之首务,反对过多阐发己意,而主张简易。“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④故朱子据详辨文义章句的宗旨,从文字、用语、句法三个层面指出南轩《癸巳论语说》的不足。
(一)文字之形音义
字、音之误。朱子指出南轩两次引文之误,一为误引伊川“思绎”为“䌷绎”。“本文作‘思绎’,今此所引改‘思’为‘䌷’。”⑤然通行本未改。二是指出“抑”字之误,“知抑精矣”,通行本改为“则益精矣。”对字音的理解决定了字义把握和义理领会,朱子《四书》于注音用心非常之细,尤关注多音多义字。如“恶”字,南轩曾读“苟志于仁无恶也”的“恶”为去声,可恶义,朱子提出当为入声,乃不善义。“盖此章恶字只是入声。”①又如南轩解默而识之为“黙识非言意之所可及,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世之言黙识者,类皆想象意度,惊怪恍惚”。朱子指出“黙识只是不假论辨而晓此亊理”,批评南轩解已流入自身所批评的“惊怪恍惚”之列,其因在于对“识”的读音有误。《集注》更倾向“识”的“志音,记义”。“不施其亲”的“施”,南轩主张尹氏说,朱子则取《经典释文》和吕氏说,认为当是“弛”字,批评谢氏释为“施报”有误。“若如谢氏,虽亦引‘无失其亲’为解,然却训‘施’为‘施报’之‘施’,则误矣。……《释文》本作‘弛’字,音诗纸反…今当从此音读。”②
字义辨析。朱子极重视字义辨析,于此批评南轩说之不足。如“罔之生”的“罔”,南轩主蒙昧义,“罔则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近于范氏“无知”说,朱子据上文主张为伊川“欺骗”说。批评南轩子绝四章的“绝而不复萌”说,认为“绝”当是“无”。言绝不言无,更显出无之程度深。南轩采纳之。朱子常以古注取代诸家说。如“人也”南轩解为“以其有人之道也”,此来自范氏“尽人道”说,朱子认为当是古注“伊人”说,南轩改从朱子。朱子判定字义诠释的标准是自然简易。如不可则止的“止”,南轩主“制止”义,朱子认为是离开义,批评其解穿凿费力。“按经文意,‘不可则止’但谓不合则去耳。……今为此说穿凿费力而不成文理。”③朱子对语气词等虚词颇用心,如不逆诈章南轩认可孔安国“先觉人情者,是宁能为贤乎”解,朱子则强烈反对,称赞杨氏说,指出“抑”为反语之词,表推测、可能关系。
“字未安”“不可晓”。朱子常以“字未(不)安”的形式指出南轩用语不妥。如南轩解敬鬼神而远之为“远而不敬,是诬而已”。朱子指出“诬字未安”,通行本改为“忽”。但朱子所批评者,南轩多未改。如“处于己者不尽也”的“处字未安”;“语乱则损志”的“损志二字未安”;“不忍乘危”的“乘危二字未安”;“包注训固为陋”说“恐亦未安”;“信于己也”的“己字未安”等。朱子批评南轩子之燕居章“圣人声气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随形”说,以形影关系阐发圣人声色之不离,并不贴切,反而有化二为一的嫌疑,未能揭示圣人与常人之别,圣之为圣所在。朱子亦批评南轩用语“不可晓”。或因太简略之故,如认为“将死而言善,人之性则然”说,“此语太略,几不可晓,恐当加详焉”①。或为表述不清而难以理解。如“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圣人所欲不存岂有一毫加于此哉”,皆认为“不可晓”。
(二)“自相矛盾”“未尽曲折”及“设问发之”
朱子指出南轩说存在前后文意自相矛盾处。如“质胜文则野”章南轩先言“与其史也宁野”,再言“矫揉就中”“修勉而进其文”,文理错杂,前后矛盾,使学者不知用力之方。“与其史也宁野”是无法做到中之后求其次,南轩则先此而后再“就中”。通行本接受批评,采取了删“矫揉就中”等做法。朱子以“语序颠倒”指出南轩说语义矛盾,如批评“仁者为能克己”颠倒了克己与仁的由工夫而本体关系。指出南轩说具有过于牵扯,“说过两节”“跨过两章”的弊病。如自行束修章先后引夫子“何莫非诲”“不保其往”说,朱子认为“此一章之中而说过两节意思,尤觉气迫而味短也”。②中人以上章引孟子“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于文意、气象皆不合,为南轩采纳。
朱子指出南轩说有“未尽曲折”“不亲切”“太支离”的弊病。如批评信近于义章“此结句似不分明,恐未尽所欲言之曲折也”③,指出“夫子听卫国之政,必自卫君之身始”说虽合理,却少曲折。批评直躬章“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实者”说“此不知所指言者谓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④,指出如患得之章“计利自便之心”说文义不分明、语意亦不亲切。通行本未改,《集编》《读书记》所引改为“患无以得之也”。批评士见危致命章引龟山说“于成人曰授命、曰见利;于士曰致命、曰见得”太支离,通行本未改。朱子亦批评南轩解无关主旨,如生而知之章“其至虽一,而其气象规模终有不同者”是多余不必要之说。
朱子在认可南轩解的同时,亦提出其需改进“发之无端”的突兀表达,建议采用“先设疑问以发之”的或问体,以实现表意自然、顺畅;明确言外之意与本文正意的区别,避免掺杂。朱子曾数次告之当采用“或问”体。如南轩以隐显、内外、本末解“一以贯之”章,朱子认为解意虽善而立言无端,导致杂乱无序,当采设问方式。指出南轩巧言令色解内容甚好,只是为言外之意,应有所引语方不显突兀,避免与经文正意的混杂,做到义理分明,并以伊川《易传》必设问以发言外义为证。“此意甚善,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此语方有所指。……如《易传》中发明经外之意,亦必设为问答以起之,盖须如此方有节次来历,且不与上文解经正意相杂。”①南轩接受之,通行本补“其心如之何”之设问句。朱子针对就有道而正焉章、克己复礼章提出同样建议,前者未改,后者采纳。
四 《论语解》改本及朱张异同
(一)《论语解》之癸巳本与淳熙本
朱子对南轩《癸巳论语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辨析,南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朱子意见,对该书加以修改,形成了与癸巳旧本差别较大的淳熙改本。②淳熙年间,南轩反复提及对《论语说》的改正,朱子、吕祖谦亦皆认可淳熙改本大优于癸巳旧本。南轩《答朱元晦》言:“《语说》荐荷指谕,极为开警。近又删改一过,续写去求教。”③朱子《张南轩文集序》言:“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晚尝更定,今已别行。”④《答吕伯恭》言:“詹体仁寄得新刻钦夫《论语》来,比旧本甚不干事。”①吕祖谦答《朱侍讲》亦言,“詹体仁近亦送葵轩《论语》来,比癸巳本益复稳密”②。
朱子《答张敬夫语解》、《癸巳论语说》引用约130条南轩《论语说》,并指出其应修改之处,如将之与通行本相较,则会认同四库馆臣仅修改23处说;如将之与《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所引南轩说相对照,即可发现半数以上实已修改。所改之处多据朱子批评,此即为淳熙改本说。真德秀《四书集编》在“子谓颜渊章”明确提出淳熙本与初本的差别。“南轩初本云:‘其行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③且详引朱子《癸巳说》批语。可见他同时见过初本与定本,且非常注意二者区别。《四书集编》引南轩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辨析朱、张异同,如不以二家定本为据,则辨析将无从展开。如多见而识,《集注》解为“识,记也。记则善恶皆当存之。”南轩为“多见而识其善”。德秀认为:“多见而识之一句,二先生所释不同,以文义求之,则南轩似优。”④“不至于谷”,朱子释“谷”为“禄”、南轩为“善”,德秀又指出,“二先生释谷之义不同,正宜参玩”⑤。至于《集注》、《或问》所引南轩说,几乎皆为朱子所赞同者,而朱子对南轩初说则多有不满,故二书所引当为改本说。此外,今本保留了二十五条作为异文的“一本”“一作”说,此“一本(作)”说除少数一、二条外,亦大体同于《集编》等所引,可知基本为淳熙修订说。遗憾的是,今中华版虽已采《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加以校勘,但仅校出约30处,据笔者考察,当有约190处。
(二)《论语解》之具体修订
四库馆臣认为南轩仅接受朱子《癸巳论语说》之23条批评,由此判定朱、张之学诚可谓“龂龂不合”,归其因为讲学家辨难习气,求胜心切使然。当“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之后,则不复相争,“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彼此“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朱、张最终“不改不争”本应显示彼此之异,馆臣反而得出“终同”的结论,盖其认为朱子癸巳对南轩之异议后皆改之,故不争,不可以朱子癸巳之见来否定南轩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①其义明显指向朱子批评之说并不可靠,是朱子改变己说而非南轩。笔者结合《集编》、《读书记》等资料,立足南轩淳熙改本,认为这一判定明显颠倒事实。南轩通行本接受、修改《癸巳说》者约为61条,而非23条。包括通行本改之、《集编》(并《读书记》、“一作”等)改之、仅《读书记》改之、仅“一作”改之等情况。且大体遵朱子意改。其中通行本所改22条;“一本”“一作”所改5条;《集编》、《读书记》引所改23条;“一作”、《集编》引改“古之学者为己”章1条;《读书记》引改“三愆”章2条;通行本略改,《集编》引大改8条。另有一半未修改者,有以下可能:南轩坚持己见未改;朱子改变看法;朱子批评本来无关紧要;南轩已改而今本未见。朱子癸巳《答张敬夫论语解》专就南轩《论语说》学而篇10章提出批评,对比《癸巳论语说》、通行本《论语解》、《四书集编》所引可知,南轩大部分据朱子意见改之。学而、巧言令色、三省章《癸巳论语说》已改之;父在观其志、信近于义、贫而无谄、不己知章通行本改之;友不如己章《集编》引改之。道千乗之国章未改,源于朱子自身思想改变。慎终追远章未改。据本人研究可知②,《集编》等所引南轩《论语》说较通行本实修改172章,诸多内容明显遵朱子之意修改,修改的共同特征是以精简为本,删繁就简,几乎每章皆有删除。修改之说在思想上与《集注》更接近,手法上更重视文义解释,风格上趋于平实,文字上更简约、精炼。综上可知,南轩淳熙本《论语解》受朱子影响很深,学术立场和观念有很大转变。进而最终认同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反思上蔡不足。《答朱元晦》言:“上蔡《语解》偏处甚多,大有害事处。”③
(三)朱张早晚异同论
南轩《论语说》受朱子影响颇深,但朱子同样受到南轩影响。二者思想异同情况颇为复杂,大体有始异终同、始同终异、始终皆同、始终皆异四种情况。“始异终同”,即朱子初批南轩而终同其说,此是朱子前后自我否定、认识逐渐加深之故。四库馆臣以三年无改章为例,指出朱子否定南轩《癸巳论语说》解,但《论语集注》采孔安国义,则与南轩说同。朱子曾认同“道千乘之国”的“道”解为“导”,《答張敬夫语解》反对南轩“治”解,后转而认可南轩解。颜渊季路侍章朱子对南轩“施”为夸张,“劳”为功劳的新说表示怀疑,倾向于施加、劳事之旧说。《集注》则以“夸大功劳”之说为第一说,保留旧说为二说,更认同南轩说。“始同终异”,即朱子早年同于(未反对)南轩说,后来则反对之。此类情况甚多,恰见出朱子思想之转进与创新。典型者如知仁动静,朱子曾以南轩仁知动静说为周子《太极图说》之意,认为“此义甚精,盖周子太极之遗意,亦已写入《集注》诸说之后矣”①。但今《集注》并无南轩说,且所论与南轩说恰相对。又如“因不失其亲”,南轩本二程说紧扣礼义而论,认为“若夫安于礼义,则此又不足以言之矣。”朱子批评南轩貌恭、言信说,但受二程、延平等影响,亦把“因不失”置于“礼义”基础上。《集注》则认为本章主旨是言行谨始而非礼义。此显出朱子说的阶段性和变易性,反映了朱子挣脱前人,独立门户之艰难。“始终皆同”,即朱子始终大体认可南轩说。《论语集注》收入南轩说8处,《四书或问》引用33处,赞赏其说“可取”、“亦佳”、“可观”等(仅“有教无类”章认为其说有得有失)。此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同时收入《集注》《或问》的三章:使民敬忠以劝、闻斯行诸、佛肸召章,此三章《癸巳论语说》亦无异议。另《或问》未提及而《集注》收入5章,表明朱子当在丁酉《或问》之后才认可南轩此说,可视为始异终同。“始终皆异”,即朱子、南轩各自坚持己见而不求苟同,如上述朱子所批评之《癸巳论语说》,通行本尚有约60条未改者,可暂视为此类。此充分体现了二者之学的特色与差异。
朱张的差异还见诸对洛学诸家的取舍上,南轩于《精义》诸家尤其是上蔡、龟山说守成较多,在诠释方法上亦是继承理学阐说大意,不屑卑近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张栻宗奉二程而罕有批评。朱子亦同样宗奉二程,但朱子此时对南轩的批评多指向上蔡而罕及二程,在此后的丁酉《或问》和己酉《集注》阶段,则对二程多有批评。盖伴随着学术方法的自觉与学术思想的自信,朱子对洛学的批判态度逐步加深,最终从义理和解释方法上超越理学,回归经学。此一一味“宗程”与适度“非程”之别,根源于朱、张在经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如将南轩《论语解》与朱子《论语集注》稍一比较,二者之别即历历在目。如《论语》首章南轩认为朋来之乐的原因是“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资已,讲习相滋,其乐孰尚”。此乃综合伊川、龟山说,《集注》则取伊川而批龟山。南轩解“不愠”为“盖为仁在已,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看似同于《集注》所引尹氏说,然朱子反对以“仁”解“学”,盖易致好高、好空、好悟的弊病。在解释方法上,朱子特别指出南轩忽视“字义”,如“学而时习之”五字,每字皆有意味,应逐字详说而不可简略。学者指出其因在于南轩之学实浸染于以二程为代表的时风习俗之中。①此外,朱子与南轩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南轩对朱子说之接受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怀,其对朱子说的拒绝和有保留地部分认可,亦见出南轩始终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虽因朱子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
(四)改本之意义
南轩《论语解》淳熙改本是在吸收朱子建议基础上,朝着精简、平实、注重文义、贴切文本的方向修改而成。是否认识到南轩《论语解》存在前后改本,直接影响对南轩思想及朱、张学术关系,甚至理学思潮演变的理解。学界对南轩《论语》思想的论述颇精,然似忽视了南轩《论语》思想前后的差别,而仅以癸巳本与通行本《论语解》立论,导致所论未尽乎善。如有学者据“博施于民”章“仁道难名,惟公近之”说论证张栻承袭明道“以公言仁”说①,而据《集编》所引、一本云,此说早已不见于淳熙改本,改本突出了仁者之心,仁者之方,其结语亦由通行本的赞颂态度(“先言仁者而后以仁之方结之,圣人之示人至矣”)转为批判语气(“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则知以博施济众言仁者,其亦泛而无统矣”)。也有学者认为,南轩《论语解》宗奉二程,大量引二程之学,举学而章引程子“时复䌷绎”说为例,淳熙本已删此说,改为“重复温绎”;据“为己为人”章“学以成已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说,指出其解合于二程,其实在朱子批评南轩以成物解成人说不妥的影响下,作为改本之说的“一本云”已删除“所谓成物”句。学者还指出“张栻《论语解》全书直接引述二程之说共32处”,此处“《论语解》”前当补“旧本”二字方确。②
五 创新与守成
朱子与南轩的学术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如中人以上章,南轩有“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南轩采用孟子“是亦所以教之”说解本章,于文意及气象皆不合。孟子不屑之教是绝之而不再教诲,本章夫子提出施教,要求就学者地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切实的教育之方,并非弃绝不教。南轩此说,有凡来学者皆告以性与天道之极之意,否则绝而不教。朱子措辞极为激烈地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而且就文本言,亦造成文意躐等断绝,气象不佳。故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其“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乃所以渐而进之,使其切问近思而自得之也”为南轩完全采纳。南轩对朱子说之接收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虚胸怀,然其对朱子说的拒绝,亦证明南轩始终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之理学家,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上所述,南轩对朱子的批评常有坚持未改者,即便接受,亦表现为有保留的部分认可而非全盘接受。如君子有恶章,朱子认为“夫子之问,未见恶人之疑;子贡之对,亦未见检身之意”。①今解已不见“恶人之疑”,而有“所以检身”说。有时尽管朱子再三苦口,南轩仍坚守己见,不为所动(当然,此仅就现存文献而论)。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论语解》为“如自孝弟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其爱虽有差等,而其心无不溥矣。”《癸巳说》采用了朱子“故孝弟立,则仁之道生”说,因朱子之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言“本立则其道生而不穷”。《集注》则解到“生”字为止,认为“无穷”字高远而不切意。本章讨论了“由孝弟可以至于仁否?”《集注》取伊川说,阐明仁与孝悌为体用、性情关系,南轩则简略认为视孝悌与仁为不同事物者失其宗旨。
朱子据其对经典诠释的新理解,主张吸收汉代章句训诂之学的长处,以纠正理学忽视文本字义之弊,而集矢于南轩《癸巳论语说》及上蔡说。南轩对朱子思想有所认同吸收,淳熙改本据其所论多有修改。在《论语》之辩中,南轩受朱子影响较大,故朱子屡称赞南轩的最大优点是闻善即迁。“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论语》旧说,某与议论修来,多是此类。”②此昭示我们应在尽量把握南轩《论语》前后改本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前后演变有整体性和连续性认识,而免于陷入对研究对象的平面化、断裂性理解。朱、张虽同宗二程而实则程度、态度有别,钱穆先生早已指出朱、张之异:“盖当时理学界风气,读书只贵通大义,乃继起立新说。……即南轩亦仍在此风气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③此为中肯之论。它提醒我们在肯认程朱理学作为一整体学派的同一性之时,亦应对其内部的差异性有所分疏。南轩在与朱子的反复交流中虽有所改变,然总体仍因袭二程理学之诠释范式。朱子则直面理学解经之弊,融合汉学、宋学解经之长,寓创新于守成之中,融经学与理学为一体,树立起新的经典典范,推动了理学的向前发展。朱、张在解经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守成之异,近则作用于湖湘学与朱子学彼此之衰退兴盛,远则关乎理学与经学之未来演变。其于今日儒学之继承与创新,亦不无启示意义。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