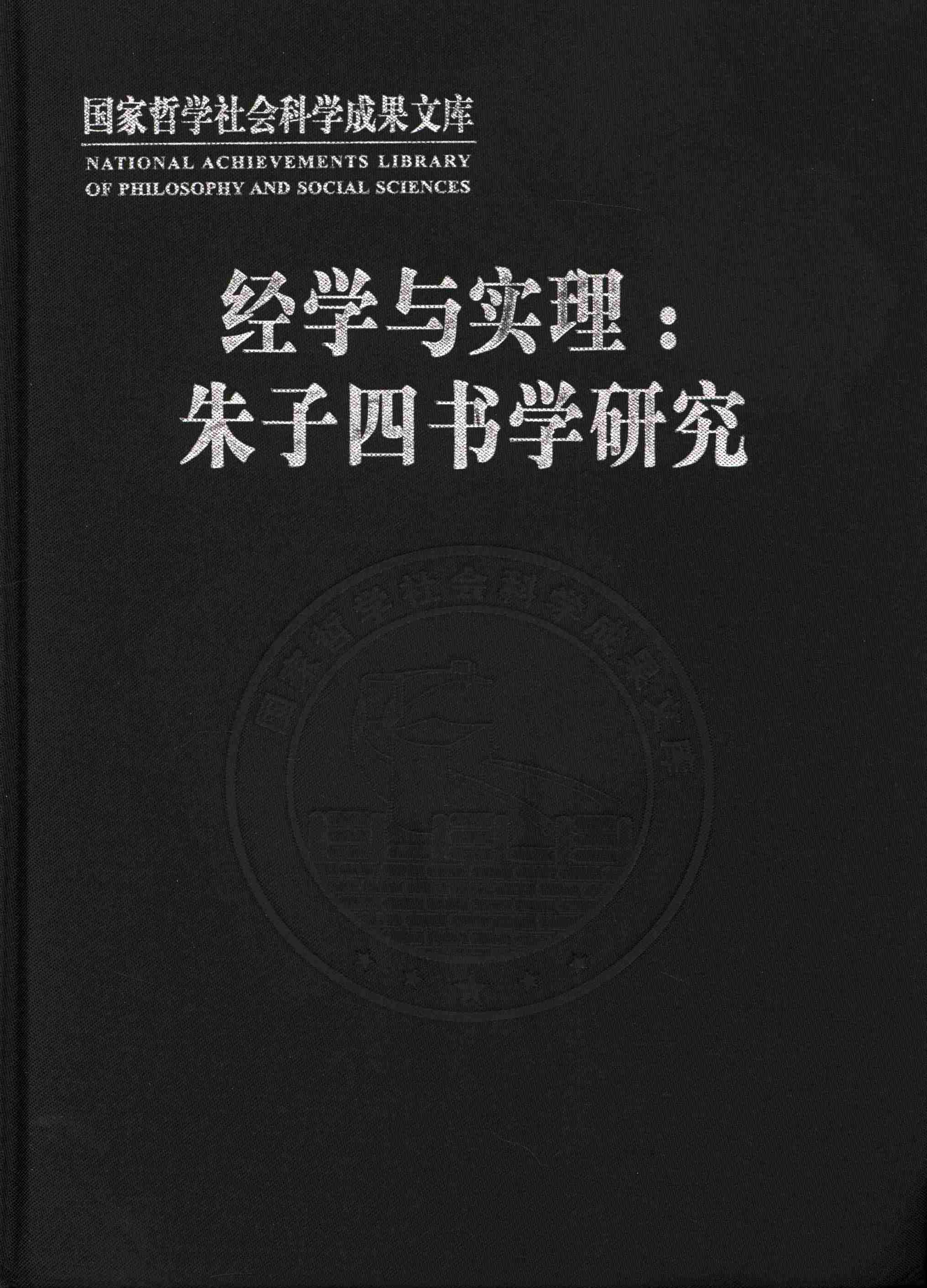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二节 求本义、发原意、砭学弊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833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求本义、发原意、砭学弊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358-36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今奉劝大家,不要随意发挥言外之意,而应注重对经文本义的诠释和理解。我们应该通过正确的训诂考据之学,深入挖掘经文的内在含义,以达到对经典原意的准确把握。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诠释文本的制约性,保持虚心状态,避免脱离文本而自立己说或者扭曲、遮蔽文本原意。只有在尊重、切合圣贤原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将诠释指向现实,针对学者为学所暴露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矫正,实现诠释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四书集注 |
内容
朱子对《四书》的诠释不仅树立了一套新的经学系统,阐述了新的为学之方,而且形成了新的诠释理论。他的诠释理论既是对汉学经学诠释的继承,亦是对宋学理学诠释的推进,是“绾经学与理学为一”(钱穆语)。概言之,朱子的《四书》诠释具有三大旨趣:一是力求切合文本原义,只有建立在理解文本内在之义基础上才可能把握文本言外之意,才真正有益于初学者,扭转“六经注我”的诠释风气。二是发明圣贤之旨,由圣贤之言,传圣贤之心。要求诠释主体保持虚心状态,尊重诠释文本的制约性。朱子极其反感脱离文本而自立己说阐发己意的做法,认为这种由述为作、反客为主的方式背离了诠释的本质,体现出对经典的不尊重,对圣贤思想的侮蔑不敬,助长了不良学风。同时朱子也反对为了维护、偏袒某人之说而扭曲、遮蔽文本原意。三是在尊重、切合圣贤之旨基础上,力求将诠释指向现实,就学者为学所暴露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矫正,“因病发药”,以实现诠释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使注本真正成为学者的良师益友。
一 求得本义
朱子认为诠释首要的追求就是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以帮助学者加深对经文的理解。他认为文本通常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字面含义,是语词表面意义,可以通过训诂解释而得,这是诠释的基础;第二重是微言大意,是文本所蕴含的言外之义,因为这种含义潜隐不露,需要诠释者发明之、彰显之。
朱子主张求得经文本义处于经典诠释第一位,提出以训诂考据之学求本义的原则,这是朱子四书诠释与宋代经典诠释主流思潮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朱子逆流而动提出这一原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文义是理解圣贤原意的前提,没有对文义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圣贤原意,盖因言以得心也。故反复强调文本之义的优先性、前提性,指出对文义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文意的把握。诠释应在正确理解文本的字面浅层语义基础上,慢慢思索虚心玩味,方能悟出深层言外文意,最终将之落实到日用工夫中。许多诠释偏离圣贤之旨的原因就在于错解文义。“圣贤之言,条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错认了他文义,则并与其意而失之耳。”①“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②
现实教学的客观效果证实表层文义与深层原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促使朱子由单一的义理解经转向兼融训诂解经。朱子最初亦崇尚义理解经,轻视训诂解经,癸未年编撰的《论语要义》一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将该书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③但教学实践证明,由于《要义》没有对经文字词句义作出训释,故学生连字面意义都很难理解,更遑论领会其中深奥性理了。有鉴于此,朱子对《要义》进行了删改,重新编成适合初学者的《论语训蒙口义》,该书着重加强了字词句的训诂考释,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标明读音,采用汉唐古注解释词义,以便于童蒙对基本语义的理解。“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④
朱子把解经明确定位成帮助读者理解经典之扶手,而不是替代读者理解的教本,故强调应加强字词名物训释上的辅助理解工作。《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中言,“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⑤批评张栻的弊病在于以己意解经,脱离文义,造成语脉的中断。非但无助于学者理解经典之义,反而加重理解难度、误导读者理解方向。“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⑥这种弊端表现在文字内容上,就是释文远远超过正文,以难解或无关之概念解释经文(如以“太极”解“性”),使读者挣扎于繁重的解文中而根本没有精力顾及经文,这也违背了前人解经的体例法则,造成了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①
朱子极力反对任意解经和以佛、老思想解经的做法,严厉批判那种不顾文本之义,扭曲圣贤原意,任意充塞个人见解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在《杂学辨》中对张九成《中庸解》、吕本中《大学解》以禅解佛思想作了批判性辨析。朱子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前辈及好友的经典诠释,指出其最大毛病在于不以文义作基础,一味发挥所谓言外之意,导致与文义冲突背离,最终偏离了圣贤本意。这种阐述即便义理再好,也不足取。他批评张栻《论语说》,“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②。“诸先生多如此说,意极亲切,但寻文义恐不然耳。”③朱子提出的忠告就是:当就文本训释入手,于自家心上体验涵养,才会得出真实见解。不要妄引诸家注释,以致于远离文本原义。
故今奉劝,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虚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说,只以训诂字义随句略解,然后反求诸心,以验其本体之实为如何,则其是非可以立判。④
所论鬼神一章全不子细,援引太多,愈觉支离,不见本经正意。可且虚心将经文熟看,甚不能晓处,然后参以章句说,教文义分明,道理便有去著。⑤
朱子坚持以求得本义为诠释的第一原则,据此对他所尊敬的二程及其弟子直接进行过多次否定。在《四书或问》中对他们批评甚多,如他对二程的执其两端说、颜子屡空说、至诚尽性说、致曲说、王天下三重说等都提出了“恐非文意”的批评。“程子以为执持过不及之两端,使民不得行,则恐非文意矣。”①《四书集注》做了大量“通训诂、正音读”以求得表层文义的工作。如在“正音读”上,他采取《经典释文》来注音,尤其注重难读词和多音多义词的标音,对“与、夫、好、恶、乐、中、知”等常用多音多义词不厌其烦地频繁标注。即以《论语集注》为例,粗略统计,下列词的注音次数分别为:“与”51次,“夫”35次,“好”30次;“焉”22字,““恶”16次,乐”,19次,“知”17次。
二 发明原意
尽管强调求本义为解经之首务,但朱子同样认识到深层文意和浅层文义在关联紧密之时,却存在一种必然的差别。由于深层文意很难以文字表达,故只能在把握浅层文义的基础上进行领悟。如关于“收放心”的诠释,朱子认为程颢之意是指“存心便是不放”,然而从文义上,只能说是将已放之心收回,是收心说。这是文义和文意作为浅层语义和深层语义所存在的必然差别。“看程先生所说,文义自是如此,意却不然。”②故朱子强调诠释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圣人之心,而不是传其言语。徒得其言而不得其心,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反之,若能得其心,则虽言语有别,并无相妨。“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依旧差了,何况犹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③
如何在求得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发明圣贤原意呢?朱子提出两大要求:
其一,诠释主体应保持虚心状态,不可以己意说经,自作文字。
受诠释者自身经历、知识素养、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即所谓“前见”④,任何诠释都难免带有诠释者的主观看法,为了达到诠释目标,首要一条是消除诠释者个人一己之见。朱子认识到诠释主体在阐述经典过程中往往抒发己意而不是文本义,特别反对诠释者以自身之意去解释经典,即“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指出这种解经未能做到由圣贤之言以求圣贤之意,而是以己意为中心,强圣贤之意以附从己说,造成本义的淹没,使得解释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放弃了对经典的尊重,丧失了诠释的本来目的,而变成个人意见的表达。朱子强调,自我表达可以通过撰写文字来体现,但是不能强借经文来发挥。
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①
怎样来保持虚心?朱子从诠释经典的体会出发,指出诠释者必须克服两个偏向:一是原有先入为主的旧说,二是原有的情感好恶。诠释主体应消除这两个偏弊,不带有任何先入旧说和个人爱憎好恶之情,以一种客观虚静的心态进入文本,做到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寻求圣贤本旨所在,达到与古圣先贤心意相通之境地。他批评《诗》、《易》等经典已被先儒穿凿附会,遮蔽了经文本意,给后学者带来很大不利。后来者的首务就是消除这种先入为主的陈旧之说,摒弃任何个人情感倾向上的爱憎喜恶,虚心研读文本,唯本文是求,如此方能得本意旨归。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①
朱子反复强调诠释不可为自身前见所蒙蔽,在进入文本之前,不应存有任何先入主见,更不可有宽己责人之私见,只有坚持客观原则,以公平开放包容之心与文本进行平等交流对话,才能寻求经文本义。“先横着一个人我之见在胸中,于己说则只寻是处,虽有不是,亦瞒过了。于人说则只寻不是处,吹毛求疵,多方驳难,如此则只长得私见,岂有长进之理!”②
不能虚心研读本文的表现之一就是以己意说经,脱离经典文本而写成阐发己意的文字,成为“作文”而不是注经。解释经典不应该令注脚成文,诠释只须疏通文意,道理自然分明通畅,不在多说。多说之弊是己意过多而经味淡薄,恰如酒中掺水,喧宾夺主,反客为主。“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义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③
表现之二就是自我膨胀,蔑视经典,贬低圣贤,虚浮狂妄,支离穿凿。“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④
表现之三是为维护圣人而过度扭曲文意,走到另一个极端。朱子在给朋友信中探讨了至德说,认为文、武实有差别,并尖锐指出这一点没有被说破的原因在于诠释者碍于圣人私情,百般曲意维护,缺乏坚持真理的标准。“此盖尊圣人之心太过,故凡百费力主张,不知气象却似轻浅迫狭,无宽博浑厚意味也。”⑤朱子认为自己此论会惊吓别人,不为他人所认同,但希望反对者能够虚心反思,体验审察,当自然有所见也。
至德之论,又更难言。……若论其志,则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处,又高于文王。若论其事,则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处圣人之不得已,而泰伯为独全其心,表里无憾也。不然,则又何以有武未尽善之叹,且以夷齐为得仁耶?前此诸儒说到此处,皆为爱惜人情,宛转回护,不敢穷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开口说。①
朱子在与吕祖约讨论“浩然之气”解时亦提出应以本文本意为主,不可牵合他说。当以公平无私之心求解,不可夹杂袒护畏敬等偏私之心。
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②
其二,尊重诠释对象,坚持文本的制约性。
朱子认为,要获得圣贤之指,就必须对诠释文本保持一种最大的敬意,这是诠释经典所应持有的态度。这种敬意体现为:树立诠释为文本服务而不是文本替诠释服务的宗旨,确立二者之间主奴宾主关系,即采用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模式。个人诠释即使再高明,也不可能超过圣贤经典,而仅仅是传达了经典原文之意。“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③同时,也不应抱有和经典相互竞争一比高低的思想,诠释与经典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二者只能是主从关系。“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鄙意于此深所未安。”④
是否尊重文本体现为诠释是否接受文本的制约,这决定了诠释效果的好坏。解经存在不少弊病,如过高、过远、过虚、过于零碎烦琐等,这些问题都和脱离文本、不受文本制约有关。“彼中议论大略有三种病:一是高,二是远,三是烦碎。以此之故,都离却本文。”①坚持文本的制约性体现在解释经典时,就是要以上下文本为根据,不可脱离具体语境。如朱子在区分《中庸》首章的“戒惧”和“慎独”时就突出了上下文的制约性。以往学者们一般不对此作出区分,认为仅仅是在谈“慎独”,朱子则视“戒惧”和“慎独”为做工夫的两个阶段。戒惧为未发之涵养,慎独为已发之提撕,并将此一区分通贯全篇,用来解释《中庸》末章所引诗句的意味。这一点曾引起张栻不满,朱子对此回应道:“‘不睹不闻’等字如此剖析,诚似支离。然不如此,则经文所谓‘不睹不闻’,所谓‘隐微’,所谓‘慎’,三段都无分别,却似重复冗长。”②接受文本制约还表现在注重文本的前后关联,具有整体通贯意识。如朱子对《中庸》首末章的呼应关系的阐发,“但首章是自里面说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处。末章却自外面一节收敛入一节,直约到里面‘无声无臭’处,此与首章实相表里也。”③
三 针砭学弊
朱子多次指出编写《集注》的目的在于为学者提供一个学习范本,使他们为学有所参照,避免走上弯路。故此,他在诠释时无论是自拟新注还是选取改造原有之注,都极为注重诠释切于日用,“因病发药”,强调诠释对不良学习方向、方法纠偏补弊的实际效果。
就总的诠释目标而言,朱子力求划清儒学与佛老虚无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学统。他早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就批评了王安石父子废弃旧说,以自身功利之说穿凿附会《论语》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只有二程独得圣人之学,其他诸说不仅穿凿者无取,即便是稍有可观者,也是未通圣道之言。“而时相父子,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之人而涂其耳目……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至于其余,或引据精密,或解析通明,非无一辞一句之可观,顾其于圣人之微意,则非程氏之俦矣。”①在此后的《论孟精义序》中,朱子进一步提出对秦汉以来为学方向的批评,低者如训诂记诵之学得言忘意,高者虽谈性理之学,却又支离破碎,未得于言。只有二程之学才传承孔孟之道,然其后学人亦有托名程氏,流入佛老,欺世误学者。朱子声称《论孟精义》之作乃是为了彰明圣学,集成众说之优长以摧折流俗佛老词章说之谬误。
《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有余家。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骛于高远者,则又支离踳驳,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学者益以病焉。……若夫外自托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然则是书之作,其率尔之诮,虽不敢辞,至于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②
这一点在《大学章句》序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朱子提出自孟子以来圣学不明,学界一直为无用的俗儒词章记诵之习,虚无寂灭的佛老之学,以及各种权谋术数功利之说所占据,直至二程上接孔孟,圣学方才得以接续。
在具体诠释上,朱子特别注意对学者日常中可能存在的为学偏差提出针砭矫正,以期收到实际效果。比如,他认为《精义》诸家之说虽然有其好处,但是过于繁乱庞杂而不精密纯粹,存在过宽之弊,容易导致学者致思为学的偏差。《集注》之作就是为了消除此弊,力求诠释的精练,以使学者思想集中于理学之路。
看文字自理会一直路去,岂不知有千蹊万径,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忒宽,易使人向别处去。某所以做个《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义。①
经文本意与日用工夫分别是衡量诠释效果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二者关联紧密,本意理解的偏离会导致日用工夫的缺失。朱子以此两个标准来衡量学者诠释工作,如他批评胡季随《中庸》首章诠释就不符合此标准,“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斗高,随语生说之过,……去本日远,以言乎经,则非圣贤之本意;以言乎学,则无可用之实功。如此讲论,恐徒纷扰,无所补于闻道入德之效也。”②胡氏对朱子提出的标准亦表认同,他在修改后的回书中,问朱子“不知经意与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可见他已经自觉按照朱子要求去做。朱子对其他学者诠释的好坏亦皆以此为评判标准。如他批评张栻对“反身而诚”的解说过高,流于咏叹,既没有发明经意,也不切合日用体验工夫,几乎与释家空虚之说无异。“此解语意极高,然只是赞咏之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若只悬空说过,便与禅家无以异矣。”③
朱子甚至将针砭学弊、切于日用工夫这一诠释原则置于其他一切原则之上。当其他诠释原则与这一原则不协调时,都得为之让步。如在精约与有利于读者理解之间,朱子就选择了后者。“‘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读者不觉,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④在关于“下学上达”的诠释中,朱子亦是如此选择,“方其学时,虽圣人亦须下学。如孔子问礼、问官名,未识须问,问了也须记。及到达处,虽下愚也会达,便不愚了。某以学者多不肯下学,故下此语。”朱子在采取诸家之说时,虽然某说有其不足,但只要该说对为学工夫具有针对性,则往往采用之。如他曾提到谢上蔡对《论语》的数条诠释虽然不很切合圣贤之意,但对于矫正学着为学之偏,具有警省之力,故此还是选择采用。“此章惟谢氏之说,切于人心,使学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①“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②
对于朱子诠释“因病发药”的这一特点,其友人弟子皆熟悉且认可。如在对“骄吝说”的注释中,潘恭叔提出朱子在本来无轻重之别的为学两弊——骄、吝之间提出本末说,明显改变了二者本无偏倚相互并列的关系,这显然有违原文之意,违背了诠释力求本义的原则。他由此推测出朱子用心在于突出“吝”比“骄”更为严重。“骄吝二字,平时作两种看。然夫子‘使骄且吝’之言,则若不分轻重者,程子‘气盈气歉’之说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复有本根枝叶之论,此说虽甚精,但与程子说不同,而以‘鄙啬’训释‘吝’字,若语意未足者。盖先生将‘吝’字看得重,直是说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处。故凡形于外者,无非私己之发。此骄之所由有如此,则工夫全在吝上。”③朱子承认特意提出骄吝为本末相因关系,目的即在于针对时弊“吝”重于“骄”而发,以引起读者注意。“此义亦因见人有如此之弊,故微发之。要是两种病痛彼此相助,但细看得吝字是阴病里证,尤可畏耳。”④“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见近来有一种人如此,其说又有所为也。”⑤
朱子自觉地将是否切于日用工夫作为修改《四书》诠释的一个主要方向。在修改中,朱子常常反思此前之说不分明,造成学者日用工夫上的缺失迷茫,使学者无法获得受用。“所论《大学》之疑甚善。但觉前日之论,颇涉倒置,故读者汨没不知紧切用功。”⑥“《中庸》所改皆是切要处,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工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觉之晚也。”⑦
综上可见,求本义、明原意、切日用是朱子诠释《四书》始终坚持的追求,尤其是针砭学弊、切于日用这一目标追求,体现出朱子坚持儒学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方面的统一,坚持儒学的实践旨归,突出儒学作为“实学”的特性,这也反映了朱子传道弘道意识的自觉定位,时刻将现实关注和学问理解融为一体,使得《四书集注》取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故继承、弘扬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就,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求得本义
朱子认为诠释首要的追求就是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以帮助学者加深对经文的理解。他认为文本通常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字面含义,是语词表面意义,可以通过训诂解释而得,这是诠释的基础;第二重是微言大意,是文本所蕴含的言外之义,因为这种含义潜隐不露,需要诠释者发明之、彰显之。
朱子主张求得经文本义处于经典诠释第一位,提出以训诂考据之学求本义的原则,这是朱子四书诠释与宋代经典诠释主流思潮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朱子逆流而动提出这一原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文义是理解圣贤原意的前提,没有对文义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圣贤原意,盖因言以得心也。故反复强调文本之义的优先性、前提性,指出对文义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文意的把握。诠释应在正确理解文本的字面浅层语义基础上,慢慢思索虚心玩味,方能悟出深层言外文意,最终将之落实到日用工夫中。许多诠释偏离圣贤之旨的原因就在于错解文义。“圣贤之言,条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错认了他文义,则并与其意而失之耳。”①“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②
现实教学的客观效果证实表层文义与深层原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促使朱子由单一的义理解经转向兼融训诂解经。朱子最初亦崇尚义理解经,轻视训诂解经,癸未年编撰的《论语要义》一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将该书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③但教学实践证明,由于《要义》没有对经文字词句义作出训释,故学生连字面意义都很难理解,更遑论领会其中深奥性理了。有鉴于此,朱子对《要义》进行了删改,重新编成适合初学者的《论语训蒙口义》,该书着重加强了字词句的训诂考释,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标明读音,采用汉唐古注解释词义,以便于童蒙对基本语义的理解。“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④
朱子把解经明确定位成帮助读者理解经典之扶手,而不是替代读者理解的教本,故强调应加强字词名物训释上的辅助理解工作。《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中言,“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⑤批评张栻的弊病在于以己意解经,脱离文义,造成语脉的中断。非但无助于学者理解经典之义,反而加重理解难度、误导读者理解方向。“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⑥这种弊端表现在文字内容上,就是释文远远超过正文,以难解或无关之概念解释经文(如以“太极”解“性”),使读者挣扎于繁重的解文中而根本没有精力顾及经文,这也违背了前人解经的体例法则,造成了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①
朱子极力反对任意解经和以佛、老思想解经的做法,严厉批判那种不顾文本之义,扭曲圣贤原意,任意充塞个人见解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在《杂学辨》中对张九成《中庸解》、吕本中《大学解》以禅解佛思想作了批判性辨析。朱子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前辈及好友的经典诠释,指出其最大毛病在于不以文义作基础,一味发挥所谓言外之意,导致与文义冲突背离,最终偏离了圣贤本意。这种阐述即便义理再好,也不足取。他批评张栻《论语说》,“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②。“诸先生多如此说,意极亲切,但寻文义恐不然耳。”③朱子提出的忠告就是:当就文本训释入手,于自家心上体验涵养,才会得出真实见解。不要妄引诸家注释,以致于远离文本原义。
故今奉劝,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虚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说,只以训诂字义随句略解,然后反求诸心,以验其本体之实为如何,则其是非可以立判。④
所论鬼神一章全不子细,援引太多,愈觉支离,不见本经正意。可且虚心将经文熟看,甚不能晓处,然后参以章句说,教文义分明,道理便有去著。⑤
朱子坚持以求得本义为诠释的第一原则,据此对他所尊敬的二程及其弟子直接进行过多次否定。在《四书或问》中对他们批评甚多,如他对二程的执其两端说、颜子屡空说、至诚尽性说、致曲说、王天下三重说等都提出了“恐非文意”的批评。“程子以为执持过不及之两端,使民不得行,则恐非文意矣。”①《四书集注》做了大量“通训诂、正音读”以求得表层文义的工作。如在“正音读”上,他采取《经典释文》来注音,尤其注重难读词和多音多义词的标音,对“与、夫、好、恶、乐、中、知”等常用多音多义词不厌其烦地频繁标注。即以《论语集注》为例,粗略统计,下列词的注音次数分别为:“与”51次,“夫”35次,“好”30次;“焉”22字,““恶”16次,乐”,19次,“知”17次。
二 发明原意
尽管强调求本义为解经之首务,但朱子同样认识到深层文意和浅层文义在关联紧密之时,却存在一种必然的差别。由于深层文意很难以文字表达,故只能在把握浅层文义的基础上进行领悟。如关于“收放心”的诠释,朱子认为程颢之意是指“存心便是不放”,然而从文义上,只能说是将已放之心收回,是收心说。这是文义和文意作为浅层语义和深层语义所存在的必然差别。“看程先生所说,文义自是如此,意却不然。”②故朱子强调诠释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圣人之心,而不是传其言语。徒得其言而不得其心,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反之,若能得其心,则虽言语有别,并无相妨。“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依旧差了,何况犹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③
如何在求得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发明圣贤原意呢?朱子提出两大要求:
其一,诠释主体应保持虚心状态,不可以己意说经,自作文字。
受诠释者自身经历、知识素养、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即所谓“前见”④,任何诠释都难免带有诠释者的主观看法,为了达到诠释目标,首要一条是消除诠释者个人一己之见。朱子认识到诠释主体在阐述经典过程中往往抒发己意而不是文本义,特别反对诠释者以自身之意去解释经典,即“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指出这种解经未能做到由圣贤之言以求圣贤之意,而是以己意为中心,强圣贤之意以附从己说,造成本义的淹没,使得解释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放弃了对经典的尊重,丧失了诠释的本来目的,而变成个人意见的表达。朱子强调,自我表达可以通过撰写文字来体现,但是不能强借经文来发挥。
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①
怎样来保持虚心?朱子从诠释经典的体会出发,指出诠释者必须克服两个偏向:一是原有先入为主的旧说,二是原有的情感好恶。诠释主体应消除这两个偏弊,不带有任何先入旧说和个人爱憎好恶之情,以一种客观虚静的心态进入文本,做到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寻求圣贤本旨所在,达到与古圣先贤心意相通之境地。他批评《诗》、《易》等经典已被先儒穿凿附会,遮蔽了经文本意,给后学者带来很大不利。后来者的首务就是消除这种先入为主的陈旧之说,摒弃任何个人情感倾向上的爱憎喜恶,虚心研读文本,唯本文是求,如此方能得本意旨归。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①
朱子反复强调诠释不可为自身前见所蒙蔽,在进入文本之前,不应存有任何先入主见,更不可有宽己责人之私见,只有坚持客观原则,以公平开放包容之心与文本进行平等交流对话,才能寻求经文本义。“先横着一个人我之见在胸中,于己说则只寻是处,虽有不是,亦瞒过了。于人说则只寻不是处,吹毛求疵,多方驳难,如此则只长得私见,岂有长进之理!”②
不能虚心研读本文的表现之一就是以己意说经,脱离经典文本而写成阐发己意的文字,成为“作文”而不是注经。解释经典不应该令注脚成文,诠释只须疏通文意,道理自然分明通畅,不在多说。多说之弊是己意过多而经味淡薄,恰如酒中掺水,喧宾夺主,反客为主。“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义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③
表现之二就是自我膨胀,蔑视经典,贬低圣贤,虚浮狂妄,支离穿凿。“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④
表现之三是为维护圣人而过度扭曲文意,走到另一个极端。朱子在给朋友信中探讨了至德说,认为文、武实有差别,并尖锐指出这一点没有被说破的原因在于诠释者碍于圣人私情,百般曲意维护,缺乏坚持真理的标准。“此盖尊圣人之心太过,故凡百费力主张,不知气象却似轻浅迫狭,无宽博浑厚意味也。”⑤朱子认为自己此论会惊吓别人,不为他人所认同,但希望反对者能够虚心反思,体验审察,当自然有所见也。
至德之论,又更难言。……若论其志,则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处,又高于文王。若论其事,则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处圣人之不得已,而泰伯为独全其心,表里无憾也。不然,则又何以有武未尽善之叹,且以夷齐为得仁耶?前此诸儒说到此处,皆为爱惜人情,宛转回护,不敢穷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开口说。①
朱子在与吕祖约讨论“浩然之气”解时亦提出应以本文本意为主,不可牵合他说。当以公平无私之心求解,不可夹杂袒护畏敬等偏私之心。
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②
其二,尊重诠释对象,坚持文本的制约性。
朱子认为,要获得圣贤之指,就必须对诠释文本保持一种最大的敬意,这是诠释经典所应持有的态度。这种敬意体现为:树立诠释为文本服务而不是文本替诠释服务的宗旨,确立二者之间主奴宾主关系,即采用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模式。个人诠释即使再高明,也不可能超过圣贤经典,而仅仅是传达了经典原文之意。“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③同时,也不应抱有和经典相互竞争一比高低的思想,诠释与经典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二者只能是主从关系。“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鄙意于此深所未安。”④
是否尊重文本体现为诠释是否接受文本的制约,这决定了诠释效果的好坏。解经存在不少弊病,如过高、过远、过虚、过于零碎烦琐等,这些问题都和脱离文本、不受文本制约有关。“彼中议论大略有三种病:一是高,二是远,三是烦碎。以此之故,都离却本文。”①坚持文本的制约性体现在解释经典时,就是要以上下文本为根据,不可脱离具体语境。如朱子在区分《中庸》首章的“戒惧”和“慎独”时就突出了上下文的制约性。以往学者们一般不对此作出区分,认为仅仅是在谈“慎独”,朱子则视“戒惧”和“慎独”为做工夫的两个阶段。戒惧为未发之涵养,慎独为已发之提撕,并将此一区分通贯全篇,用来解释《中庸》末章所引诗句的意味。这一点曾引起张栻不满,朱子对此回应道:“‘不睹不闻’等字如此剖析,诚似支离。然不如此,则经文所谓‘不睹不闻’,所谓‘隐微’,所谓‘慎’,三段都无分别,却似重复冗长。”②接受文本制约还表现在注重文本的前后关联,具有整体通贯意识。如朱子对《中庸》首末章的呼应关系的阐发,“但首章是自里面说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处。末章却自外面一节收敛入一节,直约到里面‘无声无臭’处,此与首章实相表里也。”③
三 针砭学弊
朱子多次指出编写《集注》的目的在于为学者提供一个学习范本,使他们为学有所参照,避免走上弯路。故此,他在诠释时无论是自拟新注还是选取改造原有之注,都极为注重诠释切于日用,“因病发药”,强调诠释对不良学习方向、方法纠偏补弊的实际效果。
就总的诠释目标而言,朱子力求划清儒学与佛老虚无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学统。他早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就批评了王安石父子废弃旧说,以自身功利之说穿凿附会《论语》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只有二程独得圣人之学,其他诸说不仅穿凿者无取,即便是稍有可观者,也是未通圣道之言。“而时相父子,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之人而涂其耳目……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至于其余,或引据精密,或解析通明,非无一辞一句之可观,顾其于圣人之微意,则非程氏之俦矣。”①在此后的《论孟精义序》中,朱子进一步提出对秦汉以来为学方向的批评,低者如训诂记诵之学得言忘意,高者虽谈性理之学,却又支离破碎,未得于言。只有二程之学才传承孔孟之道,然其后学人亦有托名程氏,流入佛老,欺世误学者。朱子声称《论孟精义》之作乃是为了彰明圣学,集成众说之优长以摧折流俗佛老词章说之谬误。
《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有余家。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骛于高远者,则又支离踳驳,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学者益以病焉。……若夫外自托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然则是书之作,其率尔之诮,虽不敢辞,至于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②
这一点在《大学章句》序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朱子提出自孟子以来圣学不明,学界一直为无用的俗儒词章记诵之习,虚无寂灭的佛老之学,以及各种权谋术数功利之说所占据,直至二程上接孔孟,圣学方才得以接续。
在具体诠释上,朱子特别注意对学者日常中可能存在的为学偏差提出针砭矫正,以期收到实际效果。比如,他认为《精义》诸家之说虽然有其好处,但是过于繁乱庞杂而不精密纯粹,存在过宽之弊,容易导致学者致思为学的偏差。《集注》之作就是为了消除此弊,力求诠释的精练,以使学者思想集中于理学之路。
看文字自理会一直路去,岂不知有千蹊万径,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忒宽,易使人向别处去。某所以做个《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义。①
经文本意与日用工夫分别是衡量诠释效果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二者关联紧密,本意理解的偏离会导致日用工夫的缺失。朱子以此两个标准来衡量学者诠释工作,如他批评胡季随《中庸》首章诠释就不符合此标准,“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斗高,随语生说之过,……去本日远,以言乎经,则非圣贤之本意;以言乎学,则无可用之实功。如此讲论,恐徒纷扰,无所补于闻道入德之效也。”②胡氏对朱子提出的标准亦表认同,他在修改后的回书中,问朱子“不知经意与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可见他已经自觉按照朱子要求去做。朱子对其他学者诠释的好坏亦皆以此为评判标准。如他批评张栻对“反身而诚”的解说过高,流于咏叹,既没有发明经意,也不切合日用体验工夫,几乎与释家空虚之说无异。“此解语意极高,然只是赞咏之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若只悬空说过,便与禅家无以异矣。”③
朱子甚至将针砭学弊、切于日用工夫这一诠释原则置于其他一切原则之上。当其他诠释原则与这一原则不协调时,都得为之让步。如在精约与有利于读者理解之间,朱子就选择了后者。“‘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读者不觉,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④在关于“下学上达”的诠释中,朱子亦是如此选择,“方其学时,虽圣人亦须下学。如孔子问礼、问官名,未识须问,问了也须记。及到达处,虽下愚也会达,便不愚了。某以学者多不肯下学,故下此语。”朱子在采取诸家之说时,虽然某说有其不足,但只要该说对为学工夫具有针对性,则往往采用之。如他曾提到谢上蔡对《论语》的数条诠释虽然不很切合圣贤之意,但对于矫正学着为学之偏,具有警省之力,故此还是选择采用。“此章惟谢氏之说,切于人心,使学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①“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②
对于朱子诠释“因病发药”的这一特点,其友人弟子皆熟悉且认可。如在对“骄吝说”的注释中,潘恭叔提出朱子在本来无轻重之别的为学两弊——骄、吝之间提出本末说,明显改变了二者本无偏倚相互并列的关系,这显然有违原文之意,违背了诠释力求本义的原则。他由此推测出朱子用心在于突出“吝”比“骄”更为严重。“骄吝二字,平时作两种看。然夫子‘使骄且吝’之言,则若不分轻重者,程子‘气盈气歉’之说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复有本根枝叶之论,此说虽甚精,但与程子说不同,而以‘鄙啬’训释‘吝’字,若语意未足者。盖先生将‘吝’字看得重,直是说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处。故凡形于外者,无非私己之发。此骄之所由有如此,则工夫全在吝上。”③朱子承认特意提出骄吝为本末相因关系,目的即在于针对时弊“吝”重于“骄”而发,以引起读者注意。“此义亦因见人有如此之弊,故微发之。要是两种病痛彼此相助,但细看得吝字是阴病里证,尤可畏耳。”④“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见近来有一种人如此,其说又有所为也。”⑤
朱子自觉地将是否切于日用工夫作为修改《四书》诠释的一个主要方向。在修改中,朱子常常反思此前之说不分明,造成学者日用工夫上的缺失迷茫,使学者无法获得受用。“所论《大学》之疑甚善。但觉前日之论,颇涉倒置,故读者汨没不知紧切用功。”⑥“《中庸》所改皆是切要处,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工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觉之晚也。”⑦
综上可见,求本义、明原意、切日用是朱子诠释《四书》始终坚持的追求,尤其是针砭学弊、切于日用这一目标追求,体现出朱子坚持儒学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方面的统一,坚持儒学的实践旨归,突出儒学作为“实学”的特性,这也反映了朱子传道弘道意识的自觉定位,时刻将现实关注和学问理解融为一体,使得《四书集注》取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故继承、弘扬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就,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