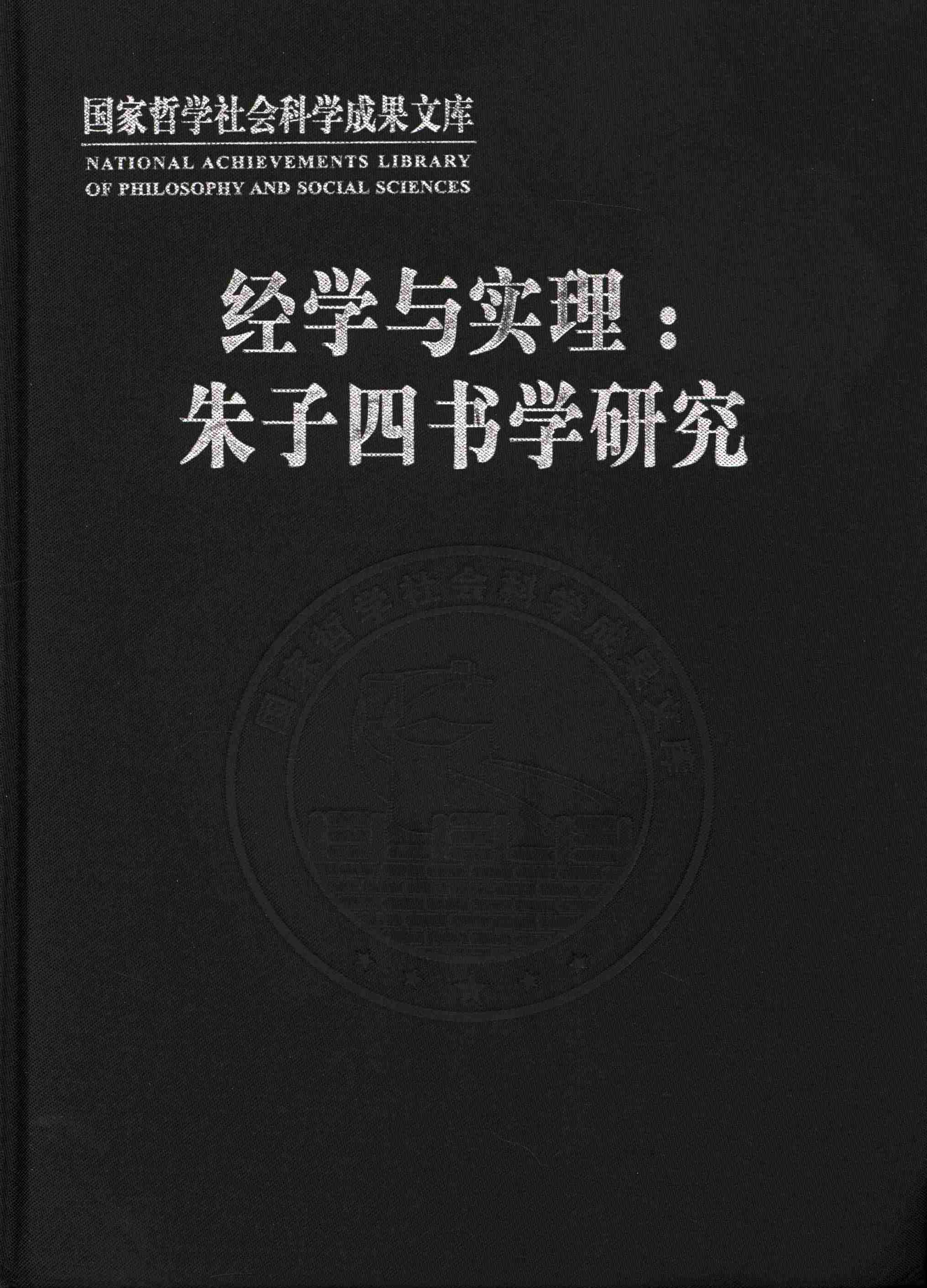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七节 本体、功夫、境界的“三位一体”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99 |
| 颗粒名称: | 第七节 本体、功夫、境界的“三位一体”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81-295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对《中庸》进行了创新性的诠释,将其建构为首尾贯通、前后相因的严密系统,并认为它集中阐发了儒家心性之奥。他将《中庸》定位为传心之书,认为首章是全书大纲,从大纲上阐发了中庸以理(中、诚)为本体,存养省察为功夫,天人合一为境界的成德系统。他强调首章作为全书大纲的统率地位,教导弟子学习《中庸》的方法,并使用“纲目之分”来贯穿全书章节、句子、词语各层次的诠释。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朱子对《中庸》从形式和义理上皆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一方面从形式上将散漫难看的《中庸》建构为首尾贯通,前后相因的严密系统,既将之“支分节解”,又使之“脉络贯通”。更重要的是在义理上,朱子将《中庸》定位为儒家传心之书,认为它集中阐发了足以与佛老异端相抗衡的儒学心性之奥。而这一心法要义在《中庸》首章中即得到充分体现。朱子认为首章乃“全书之体要”,从大纲上阐发了中庸是以理(中、诚)为本体,存养省察为功夫,天人合一为境界的“三位一体”的成德系统,此后的三十二章皆是围绕这一系统的具体展开。朱子反复强调首章作为全书大纲的统率地位,教导弟子学习《中庸》的方法,首在于分清大纲和节目,“纲目之分”也成为他贯穿全书章节、句子、词语各层次诠释的重要方法。他说:“读书先须看大纲,又看几多间架。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是大纲。夫妇所知所能与圣人不知不能处,此类是间架。”①恰当理解朱子《中庸章句》首章的义理蕴含,对掌握《中庸章句》和领会朱子心性之学,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一 成德之何以能——“道之本原出于天”
儒学作为明善成德之学,需要有一形上超越本体作为成就德性之根基,而建立这一形上超越本体的任务是由《中庸》来承担的。朱子认为此一超越本体即是性、理。《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章句》,“性即理也。”②这一天命之性即是形上超越之理,即是道之本体。它从源头上说出人物共有之本原来源于天,纯粹至善,此万物共有的本原之理,为人物展开成就自我的现实活动,达成彼此的沟通提供了动力,保证了道德超越和天人合一的可能,确保了成己成物的实现。“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③
《章句》进而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④从生成的角度对天命赋予万物的过程进行阐述,指出理从天出,当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化成就万物时,理亦随气落实于人物之中,赋予它们健顺五常之德,成为人物各自现实之性。理也就不再是那个空无依傍的虚悬在上之理了,而是与气相结合成为人物内在实存之性,其具体内容为刚健柔顺二德与仁义礼智信五种伦常德性,这样即以理沟通了天命与人(物)性,使得天人关系拉近,距离缩短,人之下学上达,内在超越之路就有了可能。理在其中起到枢纽作用,因为它“本于天而备于我”,为天人共有,兼具天理之高远超脱和性理之平实内在。
《章句》的创新在于它在吸收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摒弃了汉代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和天人观,以新的理论证成人性之善,以道德的内在超越进路来证成天人相合。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在本体论的高度重新论证天人合一,以建立道德的形上基础。朱子从理气说和天道化生的角度论述性善论,不仅强调了人与天的同质一体,而且将物也放进来,认为人、物在源头一致。这一点招致学者(包括不少朱子后学在内)的批评,如宋代陈天祥等认为人天同体彰显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神圣与尊贵,但将人、物并提,将物性与人性皆归于天命这一共同的源头,降杀了人性的独特性。真德秀则以理气同异说对此进行辩护,指出朱子兼人、物言,乃是从理同的角度论述人物所获天命,皆一而已,确保天命性善的源头。与孟子《生之谓性》章从气同理异的角度立论,突出人、物之异正好相反。
朱子在诠释中还继承了汉代以来宇宙论思想,《章句》在“五常”前增加“健顺”二字也是另一引起非议之处。朱子在回答弟子疑问时指出,“健顺”二字乃是后来修改时所加。“问:‘天命之谓性’,《章句》云‘健顺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顺’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顺’乃‘阴阳’二字。某旧解未尝有此,后来思量,既有阴阳,须添此二字始得。”①朱子增加此二字的原因在于,他根据《太极图说》中的宇宙论说,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乃是超越本体与内在现实人性之间的必要桥梁,健顺就相当于阴阳二气,五常相当于五行,既有五行,必有其源头。同时健顺与五常关系非常密切,不离不即,健统仁礼,顺统义智。《章句》与郑玄对此章的注释有相似处,可见朱子在诠释中对于汉代以来的宇宙论思想有所吸取。
《中庸》次言,“率性之谓道”。《章句》:“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②性在现实世界体现为道,人、物皆各自遵循内在本然之性,在日用事物间表现出相应的规律,这就是道。道是性的具体化,是性在日用事务之间的体现。朱子注释“率”字颇费一番功夫,前人一般将其解为以人行道,指人之修为。如“吕氏说以人行道。若然,则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诸家多作行道人上说,以率性便作修为,非也。”①朱子认为此解有误,偏离了道的意义,道并不因人之修为而在,若如此,则道乃是依附于人之物了。事实上,道无所不在,本来即有,性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故《章句》将率性解释为遵循本然之性,不假人为用力。道是自为自在的,是内在每一事物之中的具体之理,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走向,人物的行为必须遵行符合它,来不得丝毫私意作为。“‘率性之谓道’,‘率’是呼唤字,盖曰循万物自然之性之谓道。”②“率性者,只是说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许多道理。”③有意味的是,朱子经过反复思考修改的“循”说,最终还是回到了汉代的郑玄之说,郑玄正是以“循”解“率”。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偶然,朱子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回到汉代。故《章句》之创新和继承相互交错,互为隐现。
朱子对性与道的体用关系做了进一步解析,指出道和性是全体之理和具体分殊之理的关系,性是普遍全体说,道则是具体分别说。性是浑沦底,远离实际的超越本体;指“迥然孤独而言”;道是支脉,内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为行为之准则,“指著于事物之间而言”。④“性是个浑沦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条理。”⑤“性与道相对,则性是体,道是用。”⑥人物性、道本来皆同,但是在现实世界,由于气禀之差异,人的存在无法完全实现其本真状态,因而表现出种种不合理之情习陋病,遮蔽、污染了本善的人性。正因为人之一身兼具理气,使得除了圣人之外,一般人之现实存在往往为一不完善状态,天使与魔鬼、悖狂与圣神兼而备之。这就需要作后天修习之功,以变化气质,回归本然之善。此一变化气质的功夫历程,最须确定一套确实可行之矩范。此一行为标的之确立,即有赖于圣人所施之教化。允执厥中的圣人,因应于人之日用常行为而品节限定之,设立通行天下之道德准则,如礼乐、刑政之类。
下文曰:“修道之谓教”。《章句》:“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①
朱子解释了修道原因及其指向。一方面性道为人、物所共有,本源之理同,但同时人物还有先天禀赋之气相异一面,使得圣人教化十分必要。《章句》此处有两个解释引起争议。关于修道的对象,朱子认为“修道”主要就人事上说,同时又肯定亦有对物而言者,即兼人物而言。这和他对性的解释是一致的。既然人性物性皆来源于天,那么在教上也同样都有必要。朱子的这一认识也经过反复,如现存《语类》记载中就列有相互矛盾说法,有的否定教兼人物言,“问:伊川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亦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此专言人事。曰:是如此。”但朱子又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物上也要有所品节。“问《集解》中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是专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谓教’就物上亦有个品节。”②朱子最终还是肯定修道之教兼人物而有,只不过程度有所差别而已。“问‘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则‘修道之谓教’亦通人物……此是圣人教化,不特在人伦上品节防范,而及于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谓之尽物之性。但于人较详,于物较略,人上较多,物上较少。”③
对物怎么来教化呢?这就涉及到对“修”的解释。朱子将之解释为“品节”,就是节制约束之意。据此,对物的教化就是因循事物本有的自然规律来处理之,比如“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乃“就物上有所品节”。朱子批评将“修”义解释为“自修”,因为性道乃是不可修者。他同时批评学者将“教”与后文的“自明诚之谓教”说相牵合比对,二者含义不同。这个“教”的主体是圣人,乃教化义。因为人物在率性过程中往往并不能真实循性而行,总会有所偏差,戕害遮蔽本性,只有圣人才能尽性完性,故此一教之主体乃是圣人,即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圣人教化的手段包括礼乐刑政,乃德政和刑政两手皆用之意,尽管推崇德治,希望在位者正己无为而民自化,朱子从来就不反对使用刑罚、政令。然而,有学者对朱子对于教的认识不同意,如后学饶鲁就认为礼乐和刑政应该分开,刑政不属于教。其实政教在古代本来即是相通的,广义的教自可包括政。①
朱子对首章三句做了小结,“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②。强调为学功夫前提在于知人性、人道、圣人之教皆是本源于天而落实于己,天人实为一体相通,人天生就有自我超越,实现良善的潜能,若能明白此理,则下学上达之功夫自是无法遏制,精进不已。这里要注意的是,朱子用“人”字替换了“性”字,没有提到“物”,其实是为了突出人的价值自觉和自我能动性,指出天人一体,圣凡同根,人潜在的是圣人,这一个圣人需要自我去实现,体证,人应有这一份信仰和抱负。在此一成圣理想的激励下,以圣人为参照,努力自觉的朝此目标推进。
中庸首章乃全篇之大纲,首三句则是本章之大纲,本体、功夫、境界皆有所关涉,实为全篇之主旨,然其重心还是在性道本体上,阐发人先天具有的内在超越性,为日用功夫奠定根基。“此三句是怎如此说?是乃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人若能体察得,方见得圣贤所说道理,皆从自已胸襟流出,不假他求。”③朱子后学对此亦有阐发,如“北山陈氏曰:此章盖《中庸》之纲领。此三句又一章之纲领。圣贤教人必先使之知所自来而后有用力之地。”④
二 成德之所以能——“存养省察”
《中庸》在阐发性理本原之后,即转入为学功夫讨论。它首先突出了道之遍在永恒性,为下文张本,“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章句》:“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①道为理在日用常行中之显现,是具体分殊之理,此理为性之本质,为心所包含具有,乃人之内化准则。道遍在一切物中,与时空恒在,片刻离弃不得。设若可离,就不是道了,以此见出道之至广至大,无时不在。不仅主观上不可离去,客观上也不可能离弃,因为它是人物的内在本质。一方面,道具有普遍内在性、现实真实性,它内在事物与人心之中,并不脱离现实存在。同时,道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永恒性,永不间歇停止。另一方面,朱子反对“无适非道”“指物作则”说,虽然道普遍存在,但并非事事物物皆是道,那只是道之显现或载体,强调要分清物和道形上和形下两个层面,不可混通。形而下之物含有(而不是等同)形而上之道,因为道理无形,必安顿在日用事物中。如果将形而下之物视为形而上之道,那就成了佛老之学。“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朱子客观指出,儒家学者不如佛家处在于对儒道没有深刻体会,没有快乐受用之感受,仅仅在纸上理会得向上一层。儒者需要从个体独特体验中来感受道的公共普遍性,从内在实存心性中把握它的抽象超越性。
既然道为人人所本有,如何来保有体验呢?《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章句》:“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③道非一客观实存物,本就渺乎不可见,不可诉诸人之感知,但又为人真实存有,只能用心体证。为体验保有这一缥缈而又实有之精神存在,必须时刻不断保存敬畏之心,不可有丝毫懈怠间断,特别于己不睹不闻之时,尤当操存本心,戒慎恐惧。这个不睹不闻,并不仅仅指视听感官,更主要指内心意念思虑对它的感知。朱子强调不睹不闻并不是打瞌睡,而是一种特定的身体状态,“只谓照管所不到,念虑所不及处”①。这一功夫性质如何呢?戒惧功夫用于喜怒哀乐诸般情感尚未萌发之时,此存养功夫用力甚轻,不可过于执持把捉,只是提起本心,不使昏弊而已。与敬相似,但较之用敬,功夫更为轻微,不可过分用力把捉,以至操存太过,其实即是心意的贞定。“公莫看得戒慎恐惧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惊惶震惧,略是个敬模样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来,便在这里。”②
戒惧敬畏功夫于圣凡皆为必需,其差别仅在于自然与勉强,它从不见闻处这个源头一直贯穿于所见闻处,通贯动静,无时不在。朱子认为戒惧只是就功夫之普遍说,是未发存养,而更紧切处在于慎独功夫。“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章句》:“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③朱子于此句剖析极为切至,指出功夫尤当慎重于隐幽之处,微小之事上。④因为在此至隐至微,人所不知己所独知处,道并未隐没,而是昭昭显明。朱子对“几”字很重视,以“迹”和“几”“人”和“己”相对,“迹”是显露在外者,“几”乃欲发未发处,是意念、事物的征兆和分界点,在此状态下邪念虽已经蠢蠢欲动,但他人不知唯有一己良心所知,故需遏制、消除此邪念,使其在苗头状态下退出,切不可任其滋长。故朱子认为慎独乃“最紧要著功夫处”,重要即在于内心不善之迹刚刚显露他人尚未察觉时,凭一己良知自觉将之遏制消除于萌芽状态,以保持行为时时合乎道。朱子对慎独的解释亦有所承,乃是对程子和游定夫说的综合继承。“问:‘谨独’章:‘迹虽未形,几而(按:当为‘则’)已动。人虽不知,己独知之。’上两句是程子意,下两句是游氏意,先生则合而论之,是否?”曰:“然。两事只是一理。几既动,则己必知之;己既知,则人必知之。”①
《章句》此处创新在于,通过剖析戒惧和慎独,将视为修身不可或缺的两大功夫入路,对应于未发时的敬畏存养,已发时的用力省察,二者贯穿动静语默,保持了功夫的连续。“圣人教人,只此两端。”②二者目标相同,皆是为了使人之行为合于道,皆根源于人之心性情志,指向自我德性的完善,使人不受情志之偏执影响而对道有所偏离、扭曲。在具体实施上,二者相互作用,互有分工。戒惧是普遍泛说,是功夫之常,之先,“是由外言之以尽内”,是就全体动静功夫而言,是防之于未然的敬畏持守,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独则专指独处而言,是功夫之专,之后,“是由内言之以及于外”,是在戒惧未发的基础上更加紧切,于已发上透里用功,是无所不谨而谨上加谨,是察之于已然,以遏人欲之将然也。二者其实是一项功夫的不同阶段,戒惧可包含慎独,慎独乃戒惧功夫的深化,戒惧是普遍一般意义上的用工。功夫其实是从见闻处开始,一直保持到不睹不闻,这是功夫的终点,慎独不过是这整个功夫历程的中的某一阶段,是功夫全体下的部分。“戒谨恐惧是普说,言道理偪塞都是,无时而不戒谨恐惧。到得隐微之间,人所易忽,又更用谨,这个却是唤起说。”③朱子强调未发存养和已发省察乃一贯功夫,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间断,不可彼此等待推脱,以至于延误。“大抵未发已发,只是一项功夫,未发固要存养,已发亦要审察。”④“二者相捱,却成担阁。”⑤同时,朱子反复强调未发和已发仅仅是分别心之动静状态,不可太过分别,以至断为两撅,陷入僧家块然呆坐之病,批评学者“或谓每日将半日来静做功夫,即是有此病也”①。
这一剖析是朱子历经多年探究的结果,此前诸家往往将二者混同不分,滚同一气,故朱子此说一出,即遭到朋友门人的反复质问。朱子指出,从文本而言,有根据证明分说的可行性——即文中的两个连词“是故”和“故”,它们表明语义间明显有层次变化,这应是圣贤原意所在。反之,若如前辈说,混同一起则语义难以分明。“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与‘莫见乎隐’两段,分明极有条理,何为前辈都作一段衮说去?”“曰:此分明是两节事。前段有‘是故’字,后段有‘故’字。圣贤不是要作文,只是逐节次说出许多道理。若作一段说,亦成是何文字!(笔者按:‘成是’颠倒,当为‘是成’)所以前辈诸公解此段繁杂无伦,都不分明。”②而且划分的好处还在于和下文“中和”“位育”功夫正好相对应,戒惧与致中相合,慎独与致和相应,切合文脉。“如此分两节功夫,则致中、致和功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万物育’亦各有归著。”曰:“是。”③朱子将这一区分贯穿全篇,尤其在末章中也是以戒惧、慎独的切分作为中心,以结束全篇,可见这一功夫划分在《章句》中的重要性。
三 成德之最终能——“圣神功化”
《中庸》下文阐发了由此性情功夫所体现的效用,所达至的中和之境。它首先描述了何谓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章句》:“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④
朱子以心之性情,道之体用来解释中、和,指出中和就心而言,是性情之别;就道而言,是体用之分;就状态而言,是未发已发之分。喜怒哀乐之情未发为性,此状态下的心不偏不倚,处于在中状态。此一中为天下大本,为天命之性,为事物之体,天下事物之理皆由此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已发而合乎中道,不乖不戾,则为和,乃循性之谓,为道之发用。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朱子将性情与道关联起来,极大提升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人的情感价值。朱子认为,正如“道不可须臾离”一样,性情亦不可须臾离,世间万事万物皆离不开人之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人皆具有之真情实性,这普通情感即为实理流行处,道即在性情之中,性情具有内在超越的可能,可以挺立大本大原。“世间何事不系在喜怒哀乐上!……即这喜怒中节处,便是实理流行。更去那处寻实理流行。”①“中,性之德;和,情之德。”②此一性情观很有意义,破除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将性情提升到道之体用的高度,极大提升了人的尊严。《章句》在最后总结此四句时也是将性情与道相关联,“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③。人主观性情之本身即内含超越价值,与客观普遍之道相通,这也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可能。
其二,朱子对于此处曾反复进行修改,现留存的修改痕迹反映出朱子关注点的变化。朱子此前将“中”解释为“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今本删除前后句,将“心之体”改成“道之体”,差别在于心是主观,道为客观,将大本、中视为道体,突出了未发之中的超越普遍意义。就与文本关系而言,“道”也更为切合。“问:‘浑然在中’,恐是喜怒哀乐未发,此心至虚,都无偏倚,亭亭当当,恰在中间。《章句》所谓‘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④对“达道”的修改也体现出朱子认识的改变。“达”的常用义,是很好理解的“通”,朱子的未定之解突出了“达道”的自然流行贯通义,此后改为“感通”,似乎更重视人的主观作用,虽然也是讲道的自然流通,但前提是有感才通,无感不通,并不是随便自然流行。今本则改成“古今共由”,强调道的客观性,法则性,道作为时(古今)空(共由)中普遍法则,具有不可违背不可选择的先天必然性,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文本的上下呼应,如将“达道”与“循性之谓”结合。“达道,则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无不通焉’。(先生后来说达道,意不如此。)”(端蒙)①“又问:‘达’字旧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见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节,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为合当喜;怒,天下以为合当怒,只是这个道理,便是通达意。”②
其三,朱子以体用观来解释中、和、大本与达道、天命之谓性与率性之谓道的关系,这一体用观一直贯穿全篇。他在章末总结论述中和关系时,突出了二者的体用关系,认为二者动静一体,体立用行,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体,虽然有动静隐现之区别,实则是一体不分。“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③
其四,朱子剖析了中和性理的关系,指出中虚理实,中、和分别是性情之德,即性、情的本质属性,但属性不等于物体本身,不可直接将中等同于性。“‘中’是虚字,‘理’是实字,故中所以状性之体段。”④且朱子强调,不仅圣人,任何人皆有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这是生命之大本大原,圣人和凡人皆一般。差别在于已发之和上,圣人粲然显露,众人则遮蔽本性,黯然不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若论原头,未发都一般。”⑤“此大本虽庸、圣皆同,但庸则愦愦,圣则湛然。”⑥
《中庸》进而对中和境界进行了极其简洁的描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章句》却对之进行了二十倍文字的长篇论述,文字较长,可以分为两层讨论,我们先论述第一层:“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①
第一层是切近本文论述致中和的功夫效用。首先,《章句》以分析的眼光,将致中、致和以功夫形式分说,二者的效用分别对应于天地位、万物育。这一做法遭到学者的反对。当然,从文本来讲,上文既然将中和分列,则此处继承而下,未尝不可如此分说。朱子特别发挥了“致”的功夫义,认为“致”在具体用力程度所达境界是存在很大差别,学者应以极致为目标。“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②其次,本体功夫境界的一体说。朱子认为此三句,致是功夫,中和是本体,天地位、万物育是效用。关键在于功夫,由功夫透至本体,效用自然显现出来,能否透悟本体、效用大小如何皆取决于功夫。再则,人唯一可着手的只能是功夫,于本体、效用皆无有措手之地。故《章句》首先回溯到上文戒惧未发存养,慎独已发明察的功夫,进而回溯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功夫。朱子对此亦曾做过修改,我们试比较之:“致中和注云:自戒谨恐惧而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谨其独而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③前后注释相较,有同有异。主要差别在于今本更为详尽严密地描述了功夫过程,容纳了更丰富的含义,而且与文本的联系更为紧密。如前本“致中”功夫仅以“守”和“存”,今本增为先“约”,即“惟一”,约束此心归于中道归于一,然后论述“约”的状态是在“至静”下,达到“无少偏倚”,即在中的效验,进而来保守此效验而不失去。“致和”功夫也是如此。前本是“察”和“不慊”,“不慊”显然来自《大学》诚意章的自慊,强调的是个人内心自我满足愉悦的道德情感。今本将“察”换为“精”,与“惟精”相对应,然后提出功夫应体现在现实活动中“应物之处”,达到没有偏差错误的地步,即恰好的状态,而且补充“无适不然”,突出了这种状态应具有普遍性、公共性、客观性,不是局部的个体的偶然现象,可以通达于天下,即达道之义。显然,朱子关注的始终是功夫问题。此一中立不倚,天地各得其所境界的获得,离不开戒惧操存约束之功;此一和而不谬,应物合宜,无往不然,万物各得其生境界的获得,离不开隐微慎独精察之功。
第二层是对于大旨的发挥。“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①
《章句》首先阐发了获得中和效用的原因。为何一心之中和能有如此效用呢?原因就在于天人物本一体。《章句》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共禀天命之性,受阴阳五行之气,故与人实为一体。吾之心即为天地万物之心,吾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即为天地之气,吾气顺天地之气亦顺。正因为其关系如此紧密相连,故有诸己即能形于外,此其必然之功效也。进而认为此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之中和境界的获得,全在主体心性情之修养,外在效应的显露完全取决于内在修养学习之功夫,而教化之功亦自然在其中矣。
其次,《章句》指出中和乃是一体用关系,中体和用。虽然中、和分说,然而实质乃是一事。体用一原,不可偏离。体立而后用行,有无偏的未发之中,才有无谬的已发之中。反之,有和之用,则中体已在其中。这就肯定了人人皆具有中之本体,未能做到和,乃是后天功夫所致。达到此境界之前提是致中和的功夫。此处有引起质疑处,即位天地、育万物似乎是有位者的追求,常人如何能有此效用呢?朱子指出,此功夫亦是一般学者所应尽之,其效用随所处而变,事虽不同,理则一致。“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②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天地位、万物育并不重要,关键是各尽己力而已,外物并不能干扰身心之中和,天下尽管混乱,却无害于人心天地万物之安泰。
《章句》最后对首章进行了总结,“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①在此,朱子阐发了首章的语义层次及其要旨。他首先指出此章乃是子思所写下的孔门遗意。其次点明全书主旨在于儒家天理本体论、戒惧慎独功夫论和天地万物位育境界论,这三者息息相关,一体相连。其意乃在促进学者日用功夫,反身自得,存理去私,以存养推扩人性本有之善。且引杨时语点出此章居于全书体要的地位,定下了全书的基调。
《中庸章句》首章以理气论在新高度论述了古老的儒学命题“天人合一”,论证了人性善的必然与可能,完善了自孟子以来的儒家性论,并对实现自我超越的功夫论做了富有创造的阐发,确立了未发已发静存动察的功夫系统,为学者指明了修养方向。《章句》认为,中和境界的获得乃是学问修为极致所必有之效验,能否实现此一效验取决于个人心性修为,与外在地位无关。总之,《章句》首章诠释不仅阐发了一章之义理,实质上也揭示了《中庸》一书的主旨,进而可以说是非常深刻诠释了儒学乃是集本体、功夫、境界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系统对于儒学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成德之何以能——“道之本原出于天”
儒学作为明善成德之学,需要有一形上超越本体作为成就德性之根基,而建立这一形上超越本体的任务是由《中庸》来承担的。朱子认为此一超越本体即是性、理。《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章句》,“性即理也。”②这一天命之性即是形上超越之理,即是道之本体。它从源头上说出人物共有之本原来源于天,纯粹至善,此万物共有的本原之理,为人物展开成就自我的现实活动,达成彼此的沟通提供了动力,保证了道德超越和天人合一的可能,确保了成己成物的实现。“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③
《章句》进而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④从生成的角度对天命赋予万物的过程进行阐述,指出理从天出,当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化成就万物时,理亦随气落实于人物之中,赋予它们健顺五常之德,成为人物各自现实之性。理也就不再是那个空无依傍的虚悬在上之理了,而是与气相结合成为人物内在实存之性,其具体内容为刚健柔顺二德与仁义礼智信五种伦常德性,这样即以理沟通了天命与人(物)性,使得天人关系拉近,距离缩短,人之下学上达,内在超越之路就有了可能。理在其中起到枢纽作用,因为它“本于天而备于我”,为天人共有,兼具天理之高远超脱和性理之平实内在。
《章句》的创新在于它在吸收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摒弃了汉代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和天人观,以新的理论证成人性之善,以道德的内在超越进路来证成天人相合。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在本体论的高度重新论证天人合一,以建立道德的形上基础。朱子从理气说和天道化生的角度论述性善论,不仅强调了人与天的同质一体,而且将物也放进来,认为人、物在源头一致。这一点招致学者(包括不少朱子后学在内)的批评,如宋代陈天祥等认为人天同体彰显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神圣与尊贵,但将人、物并提,将物性与人性皆归于天命这一共同的源头,降杀了人性的独特性。真德秀则以理气同异说对此进行辩护,指出朱子兼人、物言,乃是从理同的角度论述人物所获天命,皆一而已,确保天命性善的源头。与孟子《生之谓性》章从气同理异的角度立论,突出人、物之异正好相反。
朱子在诠释中还继承了汉代以来宇宙论思想,《章句》在“五常”前增加“健顺”二字也是另一引起非议之处。朱子在回答弟子疑问时指出,“健顺”二字乃是后来修改时所加。“问:‘天命之谓性’,《章句》云‘健顺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顺’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顺’乃‘阴阳’二字。某旧解未尝有此,后来思量,既有阴阳,须添此二字始得。”①朱子增加此二字的原因在于,他根据《太极图说》中的宇宙论说,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乃是超越本体与内在现实人性之间的必要桥梁,健顺就相当于阴阳二气,五常相当于五行,既有五行,必有其源头。同时健顺与五常关系非常密切,不离不即,健统仁礼,顺统义智。《章句》与郑玄对此章的注释有相似处,可见朱子在诠释中对于汉代以来的宇宙论思想有所吸取。
《中庸》次言,“率性之谓道”。《章句》:“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②性在现实世界体现为道,人、物皆各自遵循内在本然之性,在日用事物间表现出相应的规律,这就是道。道是性的具体化,是性在日用事务之间的体现。朱子注释“率”字颇费一番功夫,前人一般将其解为以人行道,指人之修为。如“吕氏说以人行道。若然,则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诸家多作行道人上说,以率性便作修为,非也。”①朱子认为此解有误,偏离了道的意义,道并不因人之修为而在,若如此,则道乃是依附于人之物了。事实上,道无所不在,本来即有,性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故《章句》将率性解释为遵循本然之性,不假人为用力。道是自为自在的,是内在每一事物之中的具体之理,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走向,人物的行为必须遵行符合它,来不得丝毫私意作为。“‘率性之谓道’,‘率’是呼唤字,盖曰循万物自然之性之谓道。”②“率性者,只是说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许多道理。”③有意味的是,朱子经过反复思考修改的“循”说,最终还是回到了汉代的郑玄之说,郑玄正是以“循”解“率”。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偶然,朱子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回到汉代。故《章句》之创新和继承相互交错,互为隐现。
朱子对性与道的体用关系做了进一步解析,指出道和性是全体之理和具体分殊之理的关系,性是普遍全体说,道则是具体分别说。性是浑沦底,远离实际的超越本体;指“迥然孤独而言”;道是支脉,内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为行为之准则,“指著于事物之间而言”。④“性是个浑沦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条理。”⑤“性与道相对,则性是体,道是用。”⑥人物性、道本来皆同,但是在现实世界,由于气禀之差异,人的存在无法完全实现其本真状态,因而表现出种种不合理之情习陋病,遮蔽、污染了本善的人性。正因为人之一身兼具理气,使得除了圣人之外,一般人之现实存在往往为一不完善状态,天使与魔鬼、悖狂与圣神兼而备之。这就需要作后天修习之功,以变化气质,回归本然之善。此一变化气质的功夫历程,最须确定一套确实可行之矩范。此一行为标的之确立,即有赖于圣人所施之教化。允执厥中的圣人,因应于人之日用常行为而品节限定之,设立通行天下之道德准则,如礼乐、刑政之类。
下文曰:“修道之谓教”。《章句》:“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①
朱子解释了修道原因及其指向。一方面性道为人、物所共有,本源之理同,但同时人物还有先天禀赋之气相异一面,使得圣人教化十分必要。《章句》此处有两个解释引起争议。关于修道的对象,朱子认为“修道”主要就人事上说,同时又肯定亦有对物而言者,即兼人物而言。这和他对性的解释是一致的。既然人性物性皆来源于天,那么在教上也同样都有必要。朱子的这一认识也经过反复,如现存《语类》记载中就列有相互矛盾说法,有的否定教兼人物言,“问:伊川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亦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此专言人事。曰:是如此。”但朱子又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物上也要有所品节。“问《集解》中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是专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谓教’就物上亦有个品节。”②朱子最终还是肯定修道之教兼人物而有,只不过程度有所差别而已。“问‘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则‘修道之谓教’亦通人物……此是圣人教化,不特在人伦上品节防范,而及于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谓之尽物之性。但于人较详,于物较略,人上较多,物上较少。”③
对物怎么来教化呢?这就涉及到对“修”的解释。朱子将之解释为“品节”,就是节制约束之意。据此,对物的教化就是因循事物本有的自然规律来处理之,比如“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乃“就物上有所品节”。朱子批评将“修”义解释为“自修”,因为性道乃是不可修者。他同时批评学者将“教”与后文的“自明诚之谓教”说相牵合比对,二者含义不同。这个“教”的主体是圣人,乃教化义。因为人物在率性过程中往往并不能真实循性而行,总会有所偏差,戕害遮蔽本性,只有圣人才能尽性完性,故此一教之主体乃是圣人,即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圣人教化的手段包括礼乐刑政,乃德政和刑政两手皆用之意,尽管推崇德治,希望在位者正己无为而民自化,朱子从来就不反对使用刑罚、政令。然而,有学者对朱子对于教的认识不同意,如后学饶鲁就认为礼乐和刑政应该分开,刑政不属于教。其实政教在古代本来即是相通的,广义的教自可包括政。①
朱子对首章三句做了小结,“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②。强调为学功夫前提在于知人性、人道、圣人之教皆是本源于天而落实于己,天人实为一体相通,人天生就有自我超越,实现良善的潜能,若能明白此理,则下学上达之功夫自是无法遏制,精进不已。这里要注意的是,朱子用“人”字替换了“性”字,没有提到“物”,其实是为了突出人的价值自觉和自我能动性,指出天人一体,圣凡同根,人潜在的是圣人,这一个圣人需要自我去实现,体证,人应有这一份信仰和抱负。在此一成圣理想的激励下,以圣人为参照,努力自觉的朝此目标推进。
中庸首章乃全篇之大纲,首三句则是本章之大纲,本体、功夫、境界皆有所关涉,实为全篇之主旨,然其重心还是在性道本体上,阐发人先天具有的内在超越性,为日用功夫奠定根基。“此三句是怎如此说?是乃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人若能体察得,方见得圣贤所说道理,皆从自已胸襟流出,不假他求。”③朱子后学对此亦有阐发,如“北山陈氏曰:此章盖《中庸》之纲领。此三句又一章之纲领。圣贤教人必先使之知所自来而后有用力之地。”④
二 成德之所以能——“存养省察”
《中庸》在阐发性理本原之后,即转入为学功夫讨论。它首先突出了道之遍在永恒性,为下文张本,“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章句》:“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①道为理在日用常行中之显现,是具体分殊之理,此理为性之本质,为心所包含具有,乃人之内化准则。道遍在一切物中,与时空恒在,片刻离弃不得。设若可离,就不是道了,以此见出道之至广至大,无时不在。不仅主观上不可离去,客观上也不可能离弃,因为它是人物的内在本质。一方面,道具有普遍内在性、现实真实性,它内在事物与人心之中,并不脱离现实存在。同时,道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永恒性,永不间歇停止。另一方面,朱子反对“无适非道”“指物作则”说,虽然道普遍存在,但并非事事物物皆是道,那只是道之显现或载体,强调要分清物和道形上和形下两个层面,不可混通。形而下之物含有(而不是等同)形而上之道,因为道理无形,必安顿在日用事物中。如果将形而下之物视为形而上之道,那就成了佛老之学。“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朱子客观指出,儒家学者不如佛家处在于对儒道没有深刻体会,没有快乐受用之感受,仅仅在纸上理会得向上一层。儒者需要从个体独特体验中来感受道的公共普遍性,从内在实存心性中把握它的抽象超越性。
既然道为人人所本有,如何来保有体验呢?《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章句》:“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③道非一客观实存物,本就渺乎不可见,不可诉诸人之感知,但又为人真实存有,只能用心体证。为体验保有这一缥缈而又实有之精神存在,必须时刻不断保存敬畏之心,不可有丝毫懈怠间断,特别于己不睹不闻之时,尤当操存本心,戒慎恐惧。这个不睹不闻,并不仅仅指视听感官,更主要指内心意念思虑对它的感知。朱子强调不睹不闻并不是打瞌睡,而是一种特定的身体状态,“只谓照管所不到,念虑所不及处”①。这一功夫性质如何呢?戒惧功夫用于喜怒哀乐诸般情感尚未萌发之时,此存养功夫用力甚轻,不可过于执持把捉,只是提起本心,不使昏弊而已。与敬相似,但较之用敬,功夫更为轻微,不可过分用力把捉,以至操存太过,其实即是心意的贞定。“公莫看得戒慎恐惧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惊惶震惧,略是个敬模样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来,便在这里。”②
戒惧敬畏功夫于圣凡皆为必需,其差别仅在于自然与勉强,它从不见闻处这个源头一直贯穿于所见闻处,通贯动静,无时不在。朱子认为戒惧只是就功夫之普遍说,是未发存养,而更紧切处在于慎独功夫。“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章句》:“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③朱子于此句剖析极为切至,指出功夫尤当慎重于隐幽之处,微小之事上。④因为在此至隐至微,人所不知己所独知处,道并未隐没,而是昭昭显明。朱子对“几”字很重视,以“迹”和“几”“人”和“己”相对,“迹”是显露在外者,“几”乃欲发未发处,是意念、事物的征兆和分界点,在此状态下邪念虽已经蠢蠢欲动,但他人不知唯有一己良心所知,故需遏制、消除此邪念,使其在苗头状态下退出,切不可任其滋长。故朱子认为慎独乃“最紧要著功夫处”,重要即在于内心不善之迹刚刚显露他人尚未察觉时,凭一己良知自觉将之遏制消除于萌芽状态,以保持行为时时合乎道。朱子对慎独的解释亦有所承,乃是对程子和游定夫说的综合继承。“问:‘谨独’章:‘迹虽未形,几而(按:当为‘则’)已动。人虽不知,己独知之。’上两句是程子意,下两句是游氏意,先生则合而论之,是否?”曰:“然。两事只是一理。几既动,则己必知之;己既知,则人必知之。”①
《章句》此处创新在于,通过剖析戒惧和慎独,将视为修身不可或缺的两大功夫入路,对应于未发时的敬畏存养,已发时的用力省察,二者贯穿动静语默,保持了功夫的连续。“圣人教人,只此两端。”②二者目标相同,皆是为了使人之行为合于道,皆根源于人之心性情志,指向自我德性的完善,使人不受情志之偏执影响而对道有所偏离、扭曲。在具体实施上,二者相互作用,互有分工。戒惧是普遍泛说,是功夫之常,之先,“是由外言之以尽内”,是就全体动静功夫而言,是防之于未然的敬畏持守,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独则专指独处而言,是功夫之专,之后,“是由内言之以及于外”,是在戒惧未发的基础上更加紧切,于已发上透里用功,是无所不谨而谨上加谨,是察之于已然,以遏人欲之将然也。二者其实是一项功夫的不同阶段,戒惧可包含慎独,慎独乃戒惧功夫的深化,戒惧是普遍一般意义上的用工。功夫其实是从见闻处开始,一直保持到不睹不闻,这是功夫的终点,慎独不过是这整个功夫历程的中的某一阶段,是功夫全体下的部分。“戒谨恐惧是普说,言道理偪塞都是,无时而不戒谨恐惧。到得隐微之间,人所易忽,又更用谨,这个却是唤起说。”③朱子强调未发存养和已发省察乃一贯功夫,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间断,不可彼此等待推脱,以至于延误。“大抵未发已发,只是一项功夫,未发固要存养,已发亦要审察。”④“二者相捱,却成担阁。”⑤同时,朱子反复强调未发和已发仅仅是分别心之动静状态,不可太过分别,以至断为两撅,陷入僧家块然呆坐之病,批评学者“或谓每日将半日来静做功夫,即是有此病也”①。
这一剖析是朱子历经多年探究的结果,此前诸家往往将二者混同不分,滚同一气,故朱子此说一出,即遭到朋友门人的反复质问。朱子指出,从文本而言,有根据证明分说的可行性——即文中的两个连词“是故”和“故”,它们表明语义间明显有层次变化,这应是圣贤原意所在。反之,若如前辈说,混同一起则语义难以分明。“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与‘莫见乎隐’两段,分明极有条理,何为前辈都作一段衮说去?”“曰:此分明是两节事。前段有‘是故’字,后段有‘故’字。圣贤不是要作文,只是逐节次说出许多道理。若作一段说,亦成是何文字!(笔者按:‘成是’颠倒,当为‘是成’)所以前辈诸公解此段繁杂无伦,都不分明。”②而且划分的好处还在于和下文“中和”“位育”功夫正好相对应,戒惧与致中相合,慎独与致和相应,切合文脉。“如此分两节功夫,则致中、致和功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万物育’亦各有归著。”曰:“是。”③朱子将这一区分贯穿全篇,尤其在末章中也是以戒惧、慎独的切分作为中心,以结束全篇,可见这一功夫划分在《章句》中的重要性。
三 成德之最终能——“圣神功化”
《中庸》下文阐发了由此性情功夫所体现的效用,所达至的中和之境。它首先描述了何谓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章句》:“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④
朱子以心之性情,道之体用来解释中、和,指出中和就心而言,是性情之别;就道而言,是体用之分;就状态而言,是未发已发之分。喜怒哀乐之情未发为性,此状态下的心不偏不倚,处于在中状态。此一中为天下大本,为天命之性,为事物之体,天下事物之理皆由此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已发而合乎中道,不乖不戾,则为和,乃循性之谓,为道之发用。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朱子将性情与道关联起来,极大提升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人的情感价值。朱子认为,正如“道不可须臾离”一样,性情亦不可须臾离,世间万事万物皆离不开人之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人皆具有之真情实性,这普通情感即为实理流行处,道即在性情之中,性情具有内在超越的可能,可以挺立大本大原。“世间何事不系在喜怒哀乐上!……即这喜怒中节处,便是实理流行。更去那处寻实理流行。”①“中,性之德;和,情之德。”②此一性情观很有意义,破除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将性情提升到道之体用的高度,极大提升了人的尊严。《章句》在最后总结此四句时也是将性情与道相关联,“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③。人主观性情之本身即内含超越价值,与客观普遍之道相通,这也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可能。
其二,朱子对于此处曾反复进行修改,现留存的修改痕迹反映出朱子关注点的变化。朱子此前将“中”解释为“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今本删除前后句,将“心之体”改成“道之体”,差别在于心是主观,道为客观,将大本、中视为道体,突出了未发之中的超越普遍意义。就与文本关系而言,“道”也更为切合。“问:‘浑然在中’,恐是喜怒哀乐未发,此心至虚,都无偏倚,亭亭当当,恰在中间。《章句》所谓‘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④对“达道”的修改也体现出朱子认识的改变。“达”的常用义,是很好理解的“通”,朱子的未定之解突出了“达道”的自然流行贯通义,此后改为“感通”,似乎更重视人的主观作用,虽然也是讲道的自然流通,但前提是有感才通,无感不通,并不是随便自然流行。今本则改成“古今共由”,强调道的客观性,法则性,道作为时(古今)空(共由)中普遍法则,具有不可违背不可选择的先天必然性,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文本的上下呼应,如将“达道”与“循性之谓”结合。“达道,则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无不通焉’。(先生后来说达道,意不如此。)”(端蒙)①“又问:‘达’字旧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见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节,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为合当喜;怒,天下以为合当怒,只是这个道理,便是通达意。”②
其三,朱子以体用观来解释中、和、大本与达道、天命之谓性与率性之谓道的关系,这一体用观一直贯穿全篇。他在章末总结论述中和关系时,突出了二者的体用关系,认为二者动静一体,体立用行,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体,虽然有动静隐现之区别,实则是一体不分。“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③
其四,朱子剖析了中和性理的关系,指出中虚理实,中、和分别是性情之德,即性、情的本质属性,但属性不等于物体本身,不可直接将中等同于性。“‘中’是虚字,‘理’是实字,故中所以状性之体段。”④且朱子强调,不仅圣人,任何人皆有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这是生命之大本大原,圣人和凡人皆一般。差别在于已发之和上,圣人粲然显露,众人则遮蔽本性,黯然不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若论原头,未发都一般。”⑤“此大本虽庸、圣皆同,但庸则愦愦,圣则湛然。”⑥
《中庸》进而对中和境界进行了极其简洁的描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章句》却对之进行了二十倍文字的长篇论述,文字较长,可以分为两层讨论,我们先论述第一层:“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①
第一层是切近本文论述致中和的功夫效用。首先,《章句》以分析的眼光,将致中、致和以功夫形式分说,二者的效用分别对应于天地位、万物育。这一做法遭到学者的反对。当然,从文本来讲,上文既然将中和分列,则此处继承而下,未尝不可如此分说。朱子特别发挥了“致”的功夫义,认为“致”在具体用力程度所达境界是存在很大差别,学者应以极致为目标。“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②其次,本体功夫境界的一体说。朱子认为此三句,致是功夫,中和是本体,天地位、万物育是效用。关键在于功夫,由功夫透至本体,效用自然显现出来,能否透悟本体、效用大小如何皆取决于功夫。再则,人唯一可着手的只能是功夫,于本体、效用皆无有措手之地。故《章句》首先回溯到上文戒惧未发存养,慎独已发明察的功夫,进而回溯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功夫。朱子对此亦曾做过修改,我们试比较之:“致中和注云:自戒谨恐惧而守之,以至于无一息之不存,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谨其独而察之,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③前后注释相较,有同有异。主要差别在于今本更为详尽严密地描述了功夫过程,容纳了更丰富的含义,而且与文本的联系更为紧密。如前本“致中”功夫仅以“守”和“存”,今本增为先“约”,即“惟一”,约束此心归于中道归于一,然后论述“约”的状态是在“至静”下,达到“无少偏倚”,即在中的效验,进而来保守此效验而不失去。“致和”功夫也是如此。前本是“察”和“不慊”,“不慊”显然来自《大学》诚意章的自慊,强调的是个人内心自我满足愉悦的道德情感。今本将“察”换为“精”,与“惟精”相对应,然后提出功夫应体现在现实活动中“应物之处”,达到没有偏差错误的地步,即恰好的状态,而且补充“无适不然”,突出了这种状态应具有普遍性、公共性、客观性,不是局部的个体的偶然现象,可以通达于天下,即达道之义。显然,朱子关注的始终是功夫问题。此一中立不倚,天地各得其所境界的获得,离不开戒惧操存约束之功;此一和而不谬,应物合宜,无往不然,万物各得其生境界的获得,离不开隐微慎独精察之功。
第二层是对于大旨的发挥。“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①
《章句》首先阐发了获得中和效用的原因。为何一心之中和能有如此效用呢?原因就在于天人物本一体。《章句》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共禀天命之性,受阴阳五行之气,故与人实为一体。吾之心即为天地万物之心,吾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即为天地之气,吾气顺天地之气亦顺。正因为其关系如此紧密相连,故有诸己即能形于外,此其必然之功效也。进而认为此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之中和境界的获得,全在主体心性情之修养,外在效应的显露完全取决于内在修养学习之功夫,而教化之功亦自然在其中矣。
其次,《章句》指出中和乃是一体用关系,中体和用。虽然中、和分说,然而实质乃是一事。体用一原,不可偏离。体立而后用行,有无偏的未发之中,才有无谬的已发之中。反之,有和之用,则中体已在其中。这就肯定了人人皆具有中之本体,未能做到和,乃是后天功夫所致。达到此境界之前提是致中和的功夫。此处有引起质疑处,即位天地、育万物似乎是有位者的追求,常人如何能有此效用呢?朱子指出,此功夫亦是一般学者所应尽之,其效用随所处而变,事虽不同,理则一致。“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②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天地位、万物育并不重要,关键是各尽己力而已,外物并不能干扰身心之中和,天下尽管混乱,却无害于人心天地万物之安泰。
《章句》最后对首章进行了总结,“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①在此,朱子阐发了首章的语义层次及其要旨。他首先指出此章乃是子思所写下的孔门遗意。其次点明全书主旨在于儒家天理本体论、戒惧慎独功夫论和天地万物位育境界论,这三者息息相关,一体相连。其意乃在促进学者日用功夫,反身自得,存理去私,以存养推扩人性本有之善。且引杨时语点出此章居于全书体要的地位,定下了全书的基调。
《中庸章句》首章以理气论在新高度论述了古老的儒学命题“天人合一”,论证了人性善的必然与可能,完善了自孟子以来的儒家性论,并对实现自我超越的功夫论做了富有创造的阐发,确立了未发已发静存动察的功夫系统,为学者指明了修养方向。《章句》认为,中和境界的获得乃是学问修为极致所必有之效验,能否实现此一效验取决于个人心性修为,与外在地位无关。总之,《章句》首章诠释不仅阐发了一章之义理,实质上也揭示了《中庸》一书的主旨,进而可以说是非常深刻诠释了儒学乃是集本体、功夫、境界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系统对于儒学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