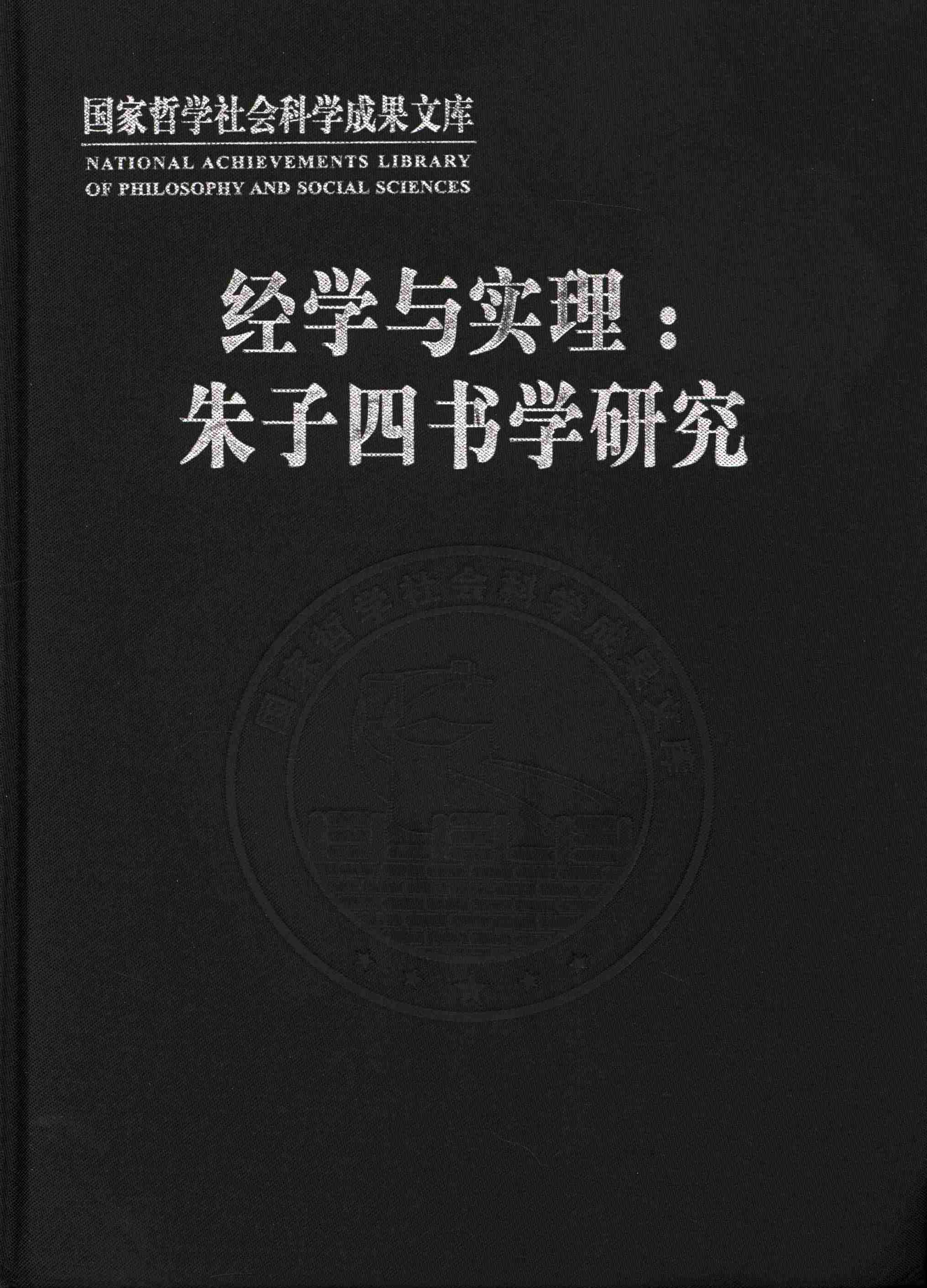二 “自欺”诠改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94 |
| 颗粒名称: | 二 “自欺”诠改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262-277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诚意之解分为“一于善”“无自欺”两层,二者关联紧密各有侧重。“一于善”是积极的挺立正面价值;“无自欺”则从消极层面,以去除遮蔽本心之善的自欺为目的。故理解“自欺”成为把握朱子诚意学的关键。事实上,朱子易箦前一两年对“自欺”修改极其频繁仔细,透露出朱子易箦前“诚意”绝笔所在。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朱子诚意之解分为“一于善”“无自欺”两层,二者关联紧密各有侧重。“一于善”是积极的挺立正面价值;“无自欺”则从消极层面,以去除遮蔽本心之善的自欺为目的。故理解“自欺”成为把握朱子诚意学的关键。事实上,朱子易箦前一两年对“自欺”修改极其频繁仔细,透露出朱子易箦前“诚意”绝笔所在。
(一)自欺之义
诚意章开篇即提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章句》对“自欺”的解释是,“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①。朱子“自欺”概念有丰富含义。首先,自欺与诚意相对,是诚意的反面,指心中意念发而不实,不自欺即是诚意。其次,自欺是涉及善恶观念的道德范畴,但它和认知有极大关联,即认识上明知善恶之别,肯认行善以去恶的正当性必要性,而在意念行为上却虚伪不实,造成知和意脱节对立。自欺最大特征即在于知和意(行)的背离关系,对这种道德认知分明,但道德行为无力,二者背离扭曲的情况,《章句》在注释“小人闲居为不善”中做了深刻阐发,“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②暗中行不善而在表面掩盖之,不愿不善行为公开化而为他人所知,证明小人尚知善恶之分和为善去恶之理,然而为内心私意所阻,难以自拔。
关于自欺的来源,朱子前期着眼于物欲之私,气禀之杂,后期着眼于知上不足,提出知上丝毫不尽都会导致自欺,“惟是知之有豪末未尽,必至于自欺”③。朱子对知的认识是复杂的,认为知有真知、半知、无知之分。据此,朱子将自欺定性为“半知”。处于自欺状态中的知善去恶其实是半知半不知,因这种知而不行,知善而不去为善,知恶而偏要行恶的知行脱节的自我欺骗行为,介于无知和真知之间。如果纯粹的不知不识,不知而行,则只能算是欺而不是自欺,并不存在知行矛盾,也不会有自我分裂对立感。如果是真知,则已经包含了行,知行是和谐一致的,自然不会出现自欺现象。“自欺是个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当为,却又不十分去为善;知道恶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爱,舍他不得,这便是自欺。不知不识,只唤做不知不识却不唤做‘自欺’”。①但是朱子在注释中极少区分知的三种含义,只是用一个“知”来表述,这就必然会带来紊乱和矛盾。照朱子对自欺的注释,自欺所引发的知行脱节显然是道德意志的无力造成了背离,病痛在行,他反复表述自欺之人“知为善以去恶”,小人也是“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故矫正功夫应在行上着手才是对症下药。但因为朱子将自欺之人的知定性为“半知”,源头在于知之不纯,故将消除自欺的功夫集中于知上,要使半知不知转化为真知纯知,见识分明了,自然就可以消除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须是见得分晓。”②但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因为尽管朱子的“真知”范畴包含了行,但行毕竟是和知相并行的独立概念,知并不能取消吞灭行,这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朱子对知的过分强调不仅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具有以知吞行的倾向,而且给实践功夫也带来不便。他明明肯定自欺是主观良好意愿和客观行为的两橛,自欺者在知上已经能够辨别善恶,肯认不是知而是内心深处所发出的意念阻断了知行的合一,使之偏离了正确轨道。这是内心意念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动力问题,故功夫本应花在意念上,意念直接主导行动,朱子自然深明此理,他也指出在知行之间的转换就是意,消除私欲实现无自欺的直接功夫在于慎独。然而他仍坚持认为功夫第一序在于致知,在分别意念之善恶的基础上,再来实行第二序的慎独功夫,以消除物欲杂念干扰,使其意念诚实。“所谓自欺者,非为此人本不欲为善去恶,但此意随发,常有一念在内阻隔住,不放教表里如一,便是自欺。但当致知,分别善恶了,然后致其谨独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杂,而后意可得其诚也。”③事实上,知行往往是反复多层相互作用互不分离的,没有离行之知,也没有无知之行。常人理解的知,是理论上起辨别是非作用的知,至于行则有专门的领域和方法,不再属于知的范围。朱子对知行本来也有明确划分,对二者关系有“知先行后,知行相须”“先知后行”“知为轻,行为重”等说。朱子也认为格物致知属于知,诚意属于行。但他同时提出的真知说是包含了知行在内的高层次的知。知行善去恶的知是表层的知,真知是深层的表里精粗无不到之知,在意念的层次里面,是否自欺就是因为有两种相反的意念在斗争,故此关键要通过知来区分意念,使得为善去恶的意念占据上风,将意念落于实处。
朱子对“自欺”的注释经过反复修改,自欺可分为两类,有意之欺还是无意之欺,特征是表里不一,知行分离、虚妄不实。具体包括这几种情况:未能纯粹至善,微有差失者;自欺之不觉者,知善恶之分不自觉滑入恶者;自欺之微者,知善恶之分,但又自我苟且自恕者;自欺之尤甚者,外善内恶。
(二)“自欺”之改
修改之一:“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
从本心明知的角度诠释自欺。据陈文蔚《通晦庵先生书问大学诚意章》可知,朱子在己酉前后曾以“心知”解释自欺,认为自欺是“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遮蔽自我本心之光明智慧。陈氏指出朱子此解是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考虑,因知有未穷,故心体有所不明,自欺之意难免发出,造成自我本心的遮蔽。“及观《章句》解自欺之说,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说,初以为疑,反复谛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盖谓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体不明而私意容或窃发,‘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自蔽其心之谓。”①朱子在回信中认为《章句》此解不如前解,过于强调了知的意味,脱离了自欺本意。己酉《答陈才卿》十四,“所喻诚意之说,只旧来所见为是。昨来《章句》却是思索过当,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②。
修改之二:“物欲之私杂乎其间”
甲寅时期从物欲私杂的角度诠释自欺。朱子甲寅年(1194年)给皇帝进讲《大学》所写《经筵讲义》一文,对“自欺”的阐发即由此入手,他说,“人心本善,故其所发亦无不善。但以物欲之私杂乎其间,是以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为自欺耳。能去其欲,则无自欺而意无不诚矣。”①朱子基于人心本善的立场,指出所发意念本来亦皆善。意念之不实源于物欲私念的纷杂惑乱,导致自欺,故消除自欺的工夫在于去除物欲之私。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将意念之善与意念之实等同之,实即善,不实即自欺。也就是把真善统一,妄杂与自欺统一。本来,意念之妄杂应与恶相应,此处与自欺相应,盖朱子认为,自欺有多层次表现,恶则是其中程度最深的一种。故妄杂与自欺相对应,语义更广泛。朱子此时提出消除自欺工夫是“去物欲之私”,立足于理欲、公私的对立,《章句》则认为自欺病根在于知行脱节,立意不同。
从物欲私杂的角度诠释自欺是朱子自欺解尚未成熟定型的表现。朱子在其他著作中亦论及之。《大学或问》即认为,“天下之道,善恶而已”。善为天命天性本心,恶则为物欲所生邪秽之物。人既受制于先天气禀,又为后天私欲所染污,故人性之善受到蒙蔽。“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则善者,天命所赋之本然;恶者,物欲所生之邪秽也。……然既有是形体之累,而又为气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②甲寅年余国秀对此提出疑问,他指出《章句》仅以“物欲”解释自欺、慎独,《或问》则兼用气禀,似有不同。朱子回应二者之别乃详略之分,并无不同。这亦充分证明《章句》在甲寅时期既以物欲之私解释“自欺”。“宋杰尝观传之六章注文释自欺、谨独处,皆以物欲为言。《或问》则兼气禀言之,似为全备。”“此等处不须疑,语意自合有详略处也。”③《语类》亦有“割去物欲之杂”说,如上引李壮祖所记,“但当致知,分别善恶了,然后致其谨独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杂,而后意可得其诚也。”④
修改之三:“若在于善而实则未能(免于)不善也”问:“‘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发若在于善,而实则未能不善也。’‘若’字之义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来一似都善,其实中心有些不爱,此便是自欺。僴。①
从似善而未能纯善的角度诠释。笔者按:此句“未能不善”之说语义颠倒,据下文“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可知“未能”与“不善”之间似夺“免于”二字,当补之。或“不”善之“不”应删去。此处朱子用“若”“实”二字相对,说明从表露在外的行为看来,似乎心之所为皆是为了善,而内在心意却没有做到纯善,夹杂了不纯粹之善,盖其心意非诚也,此即为自欺。此说强调自欺者的表里不一。此一注释相对而言似早,因为在表达表里不一、知行二致义上,后面诸修改较之“若”“实”更鞭辟有力。此处朱子还提及“前日得孙敬甫书”,批评孙氏“自慊”之说有误。
前日得孙敬甫书②,他说“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如此了然后自慊。看经文语意不是如此。“此之谓自慊”,谓“如好好色,恶恶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恶时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与自欺相对,不差豪发。所谓诚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诚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又曰:“自慊则一,自欺则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里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实有些子不愿,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诚伪之所由分也。”僩。③
朱子提出对自慊的理解应把握根本一点:自慊与自欺是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好恶无自欺的当下即是自慊,自慊乃无自欺的自然体现。二者在空间上不共存,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孙氏之误在于割裂了二者对立性,误以为二者之间还存在过渡阶段。朱子指出,诚意与自欺的对立关系亦是如此。自慊与自欺的表现是表里一致还是内外分离,即一心二心,诚伪之分。自慊是纯粹为己之学,是自快足于己也。《文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表明了类似看法,朱子曰:“但如所论,则是不自欺后方能自慊,恐非文意。盖自欺、自慊,两事正相抵背,才不自欺,即其好恶真如好好色,恶恶臭,只为求以自快自足。”①
修改之四:“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
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某意欲改作‘外为善而中实容其不善之杂’,如何?盖所谓‘不善之杂’,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着在这里,此之谓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着在这里,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认错了。只管说个‘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节,缘不奈他何,所以容在这里。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识得他源头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错了。(大概以为有纤豪不善之杂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数,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谓之金,只是欠了分数,如为善有八分欲为,有两分不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这分数。”或云:“如此,则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奈它何底。)荀子曰:‘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某自十六七读时便晓得此意。盖偷心,是不知不觉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则谋,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如公之说,这里面一重不曾透彻在。只是认得个容着,硬遏捺将去。不知得源头工夫在。”……又引《中庸》论诚处而曰,“一则诚,杂则伪”。
“只是一个心,便是诚,才有两个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他彻底只是这一个心,所以谓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间杂,便是两个心。”僴。②
从外善而内心容其不善的角度诠释。朱子师弟所争看来甚小,“未能免”和“容”虽为个别字句之差,牵涉问题却不小。其一,朱子提出“外善内恶”说而不是常用的“阴恶阳善”说,可知此处修改尚早,其根本意思还是强调表里一致。其二,此处纠缠的是知、行、善、恶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敬子的“容于不善之杂”指的是主观上知善而容恶,知行严重脱节者为自欺。如果知行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知善行善或者知恶行恶,或不知善恶而相应行善恶,则不属于自欺。知恶行善又是不可能的,故其实就是知善而行恶这种情况,才是自欺。其三,朱子批评敬子自欺是“知得了善还容着恶”,他认为自欺应该是“知得了不奈何”。敬子之说突出主观上对恶的态度问题,似乎故意纵容恶之存在、发作而不去克制;朱子的“不奈何”说则是表明主观上想去克制但客观上没有能力而导致自欺。二者之别在于自欺到底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所限。朱子认为能力的不足导致容有不善,敬子只是考虑到自欺对恶本来就抱着宽容态度,故批评敬子的“容于不善之杂”说已是第二节,但他对敬子的批评并不切合原意。其实,敬子说更符合自欺之意。朱子“无可奈何”的能力说属于意志行为,是自欺中最高一等。其四,最重要一点在于,朱子认为自欺即是自欠,是“有一豪不快于心”,“微有些没要紧底意思”,后果就是“未能免于不善”,诚意“须是十分真实为善”。他特地引荀子关于心有意识和无意识活动来证明自欺是内心无意识的流动逸出伦理规则之外。朱子反复以分量程度的差别来说明自欺,将判定自欺的标准滑到了是否做到极至,是否达于至善,这偏离了自欺本意的。为了达到这个至善,朱子又反复强调工夫源头格物知至的重要。因为朱子“知”具双重性:真知和半知,但他又没有具体点明,故使其理论看起来充满了矛盾,说自欺是“知得了不奈何”,又强调要从知上(所谓的源头上)做工夫。既然“知得了”,那自然可理解为知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应该到行上、意念上(或如敬子到态度上)去找原因和办法,但朱子还是回到知上。可见所谓“知得了”并非真的知了,而是表面的半知,故还须继续寻求真知。其五,朱子以一心之说判定诚意与自欺之别,再次强调了一心、两心的纯杂关系。一心则自慊,两心则自欺,心不可有间杂。其五,朱子此条自欺诠释已经完全从知行内外分离的角度入手,将自欺的源头推到致知上,放弃了甲寅时期的物欲之私说,表明其自欺解转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伤杂耳。某之言却即说得那个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说得是。盖知其为不善之杂而又盖庇以为之,此方是自欺。……某之说却说高了,移了这位次了,所以人难晓。……今若只恁地说时,便与那‘小人闲居为不善’处都说得贴了。”①
朱子经过一夜反思,承认敬子“容”字说对,抓住了自欺本义,即自欺是对不善虚假行为的有意识的自我纵容,而不是如他所言是无意识的过失,是未能做到极致。如此说方可平顺贴切的解释下文。朱子反思自己的“欠分数说”,“格物致知源头说”说高了,越位了,偏离了“自欺”的本义,造成理解上的晦涩,违反了诠释贴近本文的原则。而且照李敬子之解,方可将下一节文字“小人闲居为不善”贯通。
“次日又曰:夜来说得也未尽,夜来归去又思。看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段,便是连那‘毋自欺也’说。言人之毋自欺时,便要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样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谓如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小人闲居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说‘闲居为不善’,便是恶恶不如恶恶臭;‘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义都贴实平易坦然,无许多屈曲。某旧说忒说阔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样人如旧说者,欲节去之,又可惜,但终非本文之意耳。”②
朱子经过一夜反思,思想有了一大转变,认为应将“毋自欺”和下文“好好色如恶恶臭”连起来说,以声色之生理本能感受来表明道德工夫之真实自然。“斩根”之说与“一于善”相通,强调工夫的决绝有力,彻底干净。下文“小人闲居为不善”一段是作为实例从反面阐发小人的自欺,好善恶恶皆不诚意。如此一来,朱子以“自欺”为中心,打通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四者间的联系,并使得全篇文义贯通无碍,消除了此前割裂理解带来脱离本意的疏阔、高远、艰深之蔽,实践上使学者易于下手用功。“因说诚意章曰:若如旧说,是使初学者无所用其力也。”①
修改之五:“好善阴有不好以相拒,恶恶阴有不恶以相挽”
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里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谓“其好善也,阴有不好者以拒于内;其恶恶也,阴有不恶者,以挽其中。”盖好恶未形时,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恶底藏在里面了。”②朱子还曾用“好善阴有不好”“恶恶阴有不恶”来诠释“小人闲居不善”之内外对立的情形。虽知好善,然内心则阴有不好善之意以拒绝善;虽知恶恶,然内心有不恶之意以挽留恶。此为未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者,在好善恶恶上未能做到表里如一,内外一如,故体现为意念的心理拉锯之战而终不免于自欺者,与敬子所言,“容其不善”,朱子所言“不奈何”相通。此说虽为吕涛己未所记,但应为朱子此前之说,盖《大学或问》已言之,不过《或问》未用“阴”这个词而已,《或问》更强调了真知的重要。“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则其好善也,虽曰好之而未能无不好者以拒之于内。不知恶之真可恶,则其恶恶也,虽曰恶之而未能无不恶者以挽之于中。”③
修改之六:“为恶于隐微之中,诈善于显明之地”
以隐恶显善之说解释“小人闲居为不善”。朱子早在甲寅之《讲义》中即以“为恶于隐微之中,诈善于显明之地”的对比手法,突出小人自欺之甚的特点。小人未能慎独,故于隐微之中行其恶,而在显明之处行其善,其恶为真恶,善为伪诈之善,欺人之善。善、恶,显、微、内、外、虚、实形成一组鲜明对比,尽显小人自欺欺人之情态。《讲义》注:“小人为恶于隐微之中,而诈善于显明之地,则自欺之甚也。”沈僴所录《语类》中,朱子仍提起此说,可见朱子修改之中亦有其一致连贯性。“所谓为恶于隐微之中,而诈善于显明之地,是所谓自欺以欺人也。”①此说朱子随即以阴阳善恶之对比形式取代之,但“诈善”之说《章句》仍保留之,“欲诈为善卒不可诈”。
修改之七:“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与“阳善阴恶,好善恶恶”
“问:诚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旧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发,阳善阴恶,则其好善恶恶,皆为自欺而意不诚矣。’恐初读者不晓。又此句《或问》中己言之,却不如旧注云:‘人莫不知善之当为,然知之不切,则其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故欲诚其意者无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晓。”曰:“不然,本经正文只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说。今若引致知在中间,则相牵不了,却非解经之法。又况经文‘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说话极细。盖言为善之意,稍有不实,照管少有不到处,便为自欺,未便说到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处。若如此则大故无状,有意于恶,非经文之本意也。所谓‘心之所发,阳善阴恶’,乃是见理不实,不知不觉地陷于自欺,非是阴有心于为恶而诈为善以自欺也。”僴。②
朱子此处讨论了诠释视角“致知”与“好善恶恶”。弟子认为“自欺”的今注不如旧注明白易懂,旧注提出,人虽知善之当为,但因非真切之知,故其心所发出之意,必定有阴恶阳善以自欺者。因此诚意工夫在于禁止此阴恶阳善之意的发出。朱子提出三点反驳,一是旧注之解着眼于致知,突出因无真知,故所发之意有阴恶阳善者。而“诚意”章中本无致知之义,将“致知”掺杂于诚意之中,脱离本文原意,侵占了诚意地位,犯有诠释牵合越位之弊。新注符合原文应有之意,与解经当求本意的原则相一致。二是就语义而言,旧、新注语意轻重有别,新注“阳善阴恶,好善恶恶”之说更符合原义。自欺所指意思极为精细,是说人本心存善意,只是在行为、意念上的稍微放松不留神,认识上的“见理不实”,而不自觉的流于自欺,造成表里不一、内外乖张,其本心并非如此。这种自欺的程度很低,是“微有差失”,是“无心之失”,可说是君子之过。旧注“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之说是此人本心即要为恶,而不过以善掩盖而已,这是“存心为恶”,是“大故之恶”,简直是恶人之恶了。如此就语义太重,属于自欺里面最严重的一种,指那种极为明显的大恶。今本所改则相当于最轻微的那种无心而流于自欺者,是从细微无意识处而言,故说工夫极细,这才是原文之意。其三,旧注不当连带下文“小人闲居为不善”来说,“小人闲居为不善”乃是自欺之大者。新注、旧注的主要差别在于从何角度(粗还是细)来理解自欺,朱子的修改趋向于细,认为自欺可能仅仅是君子之过,到小人地步已不是自欺所能概括,已是到了恶的地步,反映出他对于自欺的认识发生了由外在之恶到内在之失的变化。旧新注的另一个差别是,新注没有连“毋”一起说,旧注则牵连一起。在笔墨上,旧注用字50,较今注多出一倍,违背诠释简约精当之原则。从这条讨论亦可看出,朱子自欺诠释从“物欲”转入“致知”后,再次发生变化,转向尽量地切近文本。
朱子此一新注,沈僴于《语类》中还有记载: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发,阳善阴恶,则其好善恶恶,皆为自欺而意不诚矣。”①
此注和旧注相比,删除了“致知”的掺杂,而增强了本章上下文之间的关联,即增加了他在与李敬子讨论时提出的“自欺”应与下文“好善恶恶”相关联的看法,此注与《章句》相比,仍有不少差异处。其一,因为在“毋自欺中”并无“阳善阴恶”之意,考虑到与原文本意的和谐,故《章句》将“阳善阴恶”之说移到了下一节“小人见君子而后厌然”的注释中,以此专指小人之自欺,即程度严重之自欺。“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其二,《章句》突出了知、意脱节的问题,强调了诚意工夫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同时仍保留了致知与自欺的紧密关联,“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此是对旧注“人莫不知善之当为”的回归,此处新注“阳善阴恶”仅反映出表里不一致,没有强调知在诚意中的先决性作用,未能从根源上指出自欺的病因。其三,《章句》和旧注的共同点在于皆表明自欺是就一己之隐微意念而言,是个人私下的个体性活动,自欺是知行分离,这种分离在程度上极为轻微。其四,《章句》诠释更为精练。
修改之八:“则无待于自欺而意无不诚也”
又问:“今改注下文云:‘则无待于自欺而意无不诚也’,据经文方说‘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辞’,若说‘无待于自欺’,恐语意太快,未易到此。”僴。①
此句注释不见于《章句》,已删之。弟子认为“无待于自欺”的说法在语义上伤快,与经文“毋(禁止)自欺”之义不合。朱子的辩解是,既然能够禁止不自欺,说明已经能知理之是非,自觉行好善恶恶工夫,使意念之发纯善无恶,由此即可达到不自欺,“毋自欺”虽有禁止义,但不自欺之状态,并非勉强控制所能达到。朱子以人受寒病肚子为譬,说明知上分晓善恶在工夫上的重要。其实朱子之说并不合原意,工夫是无限反复的过程,不可以说不做禁止自欺的工夫。再就经文意思来看,毋自欺和无待自欺是有差距的,从“无待自欺”看不出工夫,而只是工夫达到后的一种境界、效用罢了。
修改之九:“假托”还是“掩覆”
国秀问:“《大学》诚意,看来有三样。一则内全无好善恶恶之实,而专事掩覆于外者,此不诚之尤也;一则虽知好善恶恶之为是,而隐微之际,又苟且以自瞒底;一则知有未至,随意应事,而自不觉陷于自欺底。”曰:“这个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浅之不同耳。”焘。
次早云:“夜来国秀说自欺有三样底,后来思之,是有这三样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浅深之不同。”又因论以“假托”换“掩覆”字云:‘假托’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轻,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论诚与不诚不特见之于外,只里面一念之发,便有诚伪之分。”①
余国秀提出不诚自欺有三种情况:其一,自欺之尤者,专事掩覆于外,完全无丝毫行善去恶之实;其二,自欺之微者,知善恶之分,但隐微之际又苟且自恕,意有不诚者;其三,自欺之不觉者,受知识所限,未能分辨善恶而不自觉滑入自欺者。朱子开始认为不需要做此分别,三者性质皆同,都是自欺,只是情况有深浅之别。后来反思确实存在这三种情况,但又指出皆是同一性质下的浅深之别。朱子又和余国秀讨论用“假托”还是“掩覆”描述“自欺”,二者形容自欺形状,畸轻畸重,难得恰好。此两字今本皆不用。朱子对自欺之类型亦略有分别,如他指出自欺的表现:内外分离,表现为为人之学,与为己相对;有始无终懈怠之学,与自始至终的彻底连续性不同;九分善,一分苟且之学,缺乏纯粹性。诚意之学则应表里如一,内外彻底,纤毫不违,为己不苟。“凡恶恶之不实,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实不然,或有所为而为之,或始勤而终怠,或九分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实而自欺之患也。所谓诚其意者,表里内外彻底皆如此,无纤豪丝发苟且为人之弊。”②
据以上修改历程可知,朱子在围绕自欺的多次修改中,认识有很大变化,己酉年曾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说,突出了致知对于诚意的重要性;甲寅时期侧重“物欲之私”解释,着眼天理人欲的分裂;此后转向知行背离、内外对立、阴阳割裂的角度诠释,期间很注意把握致知与诚意、自欺之程度等问题,屡有调整。丙辰至戊午年间提出“若在于善而实则未能”说,以“若、实”表明内外的背离,后又改为“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此一“中外善恶”的“纯杂”背离说有一定代表性。此后朱子又先后提出“阴阳善恶”说,前一次从致知说自欺,认为“知之不切”导致“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此种“阴恶阳善”者乃有意为恶,为自欺中最严重者。后一次修改去除了“知之不切”,提出“阳善阴恶”说,认为自欺是无心之过,为自欺中最轻微者,而且以至善的要求来看待自欺与否,将自欺认定为“自欠”,是知上有丝毫未尽所造成的,“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处”,便是自欺,这拔高了对自欺的认识。阴阳善恶说在朱子自欺说中也颇具代表性。此后,朱子还提出“无待于自欺而意无不诚”说,此说亦过于强调知的意义,且与本文“毋”的禁止意有所背离。到去世前一年的己未年,朱子还在讨论自欺之类别,探讨用“假托”还是“掩覆”解释自欺,文中有“掩其不善”说,朱子最终倾向用“掩”字,《章句》即用了“掩”和“诈”的对说。
据朱子对自欺的繁复修改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即朱子诚意之解的根本线索是意念之善与恶的关系。无论哪一次修改,总是围绕善与恶展开。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胡炳文等提出的“一于善”说更符合朱子本章修改之历程,它揭示了诚意的根本特质。朱子颇为重视的《大学或问》亦是着力阐发善恶,开篇即点出本章之旨围绕善恶展开,“天下之道,善恶而已”。诚意章最后以“故君子必诚其意”重复之说结束全章,《章句》之解,仍然落实于意念之善,“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结之”①。《语类》指出诚意最紧要,紧要处在于诚意乃是分别善恶关节处,故最要用力。“要紧最是诚意时节,正是分别善恶,最要着力。”②“一于善”说正是鲜明的揭示诚意归于善的根本特色。
(三)自慊与自欺
反观朱子对“自慊”的认识,虽有提及,但并非核心问题。朱子长期以来,仅注重“自慊”的个别意义,并未将之与诚意、自欺之解相联系。直到《经筵讲义》之时,仍只是将之与“毋自欺”相连。过了几年,朱子方才意识到应该将“自慊”“慎独”与“自欺”一起,纳入诚意的体系中。《经筵讲义》将诚意章第一部分切分为二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为第一层,于“毋自欺”后断开随文解释;“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为第二层,而且“自慊”与“慎独”亦未关联解释,各自独立一句。①今本《章句》则从开头“所谓”一直到“慎其独”连起来讲,《讲义》断开为二,表明朱子此时没有认识到诚意包含自欺、自慊、慎独三个要点,将它们前后割裂,对诚意的阐发缺少一种有力例证和说明,而且在文势上也不连贯。朱子戊午《答孙敬甫》一书,仍未以“自欺”将诸概念串联起来。如他认为,诚意即是不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说明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则为单独一节。“故其文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继之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实。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谓自慊,即是言如恶恶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谓必如此而后能自慊也。所论谨独一节,亦似太说开了。”②上文“自欺”修改四所引《语类》反映出朱子去世前一两年在与李敬子反复讨论自欺修改中,方才反思应将自慊、慎独纳入诚意范围下。
比较《讲义》、《或问》、《章句》,对自慊、慎独之解并无差别,差别在于自欺,《讲义》侧重好恶深切,意常快足而无自欺。即自慊而无自欺,即陈栎所主张的“必自慊而无自欺”。
《讲义》:“臣熹曰:如恶恶臭,恶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之地也。好善恶恶深切如此,则是意常快足而无自欺矣。”③
《章句》:“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①
《章句》加大了“自欺”的阐发,首先即指出诚意是自修之事,“致知”对于诚意自修具有不可或缺的先在性,必须在知上分别善恶,方能在行上用力。诚意独立于致知的意义在于,光有致知是不够的,必须落实于自身的切己行动,此一行动要求真诚向内,坚决果敢,彻底为己,而自慊是包含于其中的一个效验,不具有工夫意义。《章句》与《讲义》的差别在于,《章句》深入细致剖析了诚意毋自欺的工夫,即阐明了诚意工夫的理论前提、实际操作、必然效用。《讲义》“意常快足而无自欺”之类的说法仅仅侧重诚意之效用,过于轻快,亦使学者无所用力。故此类说法《章句》均不见之。
与耗尽心力诠释“自欺”相反,朱子有意删除了《章句》有关“自慊”之解。如朱子对《或问》此章的修改,即删除了此前所引的程子自慊之说,认为程子之说过头了。问:“《或问》‘诚意’章末,旧引程子自慊之说,今何除之?”曰:“此言说得亦过。”②程子之说为,“人须知自慊之道,自慊者,无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则张子厚所谓‘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程子认为自慊则无不足,自然无自欺了,引张载说指出若有不足,则表明心仍在外,杂念私欲未尽,故意未诚,心未专一也。朱子反思此说过高,拔高了自慊的意义。而据曾祖道丁巳(1197年)所记《语类》,朱子尚将自慊理解为无不足,并引横渠之说为证,由此可知陈淳所记上条,乃是己未所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慊者,无不足也。如有心为善,更别有一分心在主张他事,即是横渠所谓‘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③
(一)自欺之义
诚意章开篇即提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章句》对“自欺”的解释是,“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①。朱子“自欺”概念有丰富含义。首先,自欺与诚意相对,是诚意的反面,指心中意念发而不实,不自欺即是诚意。其次,自欺是涉及善恶观念的道德范畴,但它和认知有极大关联,即认识上明知善恶之别,肯认行善以去恶的正当性必要性,而在意念行为上却虚伪不实,造成知和意脱节对立。自欺最大特征即在于知和意(行)的背离关系,对这种道德认知分明,但道德行为无力,二者背离扭曲的情况,《章句》在注释“小人闲居为不善”中做了深刻阐发,“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②暗中行不善而在表面掩盖之,不愿不善行为公开化而为他人所知,证明小人尚知善恶之分和为善去恶之理,然而为内心私意所阻,难以自拔。
关于自欺的来源,朱子前期着眼于物欲之私,气禀之杂,后期着眼于知上不足,提出知上丝毫不尽都会导致自欺,“惟是知之有豪末未尽,必至于自欺”③。朱子对知的认识是复杂的,认为知有真知、半知、无知之分。据此,朱子将自欺定性为“半知”。处于自欺状态中的知善去恶其实是半知半不知,因这种知而不行,知善而不去为善,知恶而偏要行恶的知行脱节的自我欺骗行为,介于无知和真知之间。如果纯粹的不知不识,不知而行,则只能算是欺而不是自欺,并不存在知行矛盾,也不会有自我分裂对立感。如果是真知,则已经包含了行,知行是和谐一致的,自然不会出现自欺现象。“自欺是个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当为,却又不十分去为善;知道恶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爱,舍他不得,这便是自欺。不知不识,只唤做不知不识却不唤做‘自欺’”。①但是朱子在注释中极少区分知的三种含义,只是用一个“知”来表述,这就必然会带来紊乱和矛盾。照朱子对自欺的注释,自欺所引发的知行脱节显然是道德意志的无力造成了背离,病痛在行,他反复表述自欺之人“知为善以去恶”,小人也是“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故矫正功夫应在行上着手才是对症下药。但因为朱子将自欺之人的知定性为“半知”,源头在于知之不纯,故将消除自欺的功夫集中于知上,要使半知不知转化为真知纯知,见识分明了,自然就可以消除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须是见得分晓。”②但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因为尽管朱子的“真知”范畴包含了行,但行毕竟是和知相并行的独立概念,知并不能取消吞灭行,这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朱子对知的过分强调不仅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具有以知吞行的倾向,而且给实践功夫也带来不便。他明明肯定自欺是主观良好意愿和客观行为的两橛,自欺者在知上已经能够辨别善恶,肯认不是知而是内心深处所发出的意念阻断了知行的合一,使之偏离了正确轨道。这是内心意念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动力问题,故功夫本应花在意念上,意念直接主导行动,朱子自然深明此理,他也指出在知行之间的转换就是意,消除私欲实现无自欺的直接功夫在于慎独。然而他仍坚持认为功夫第一序在于致知,在分别意念之善恶的基础上,再来实行第二序的慎独功夫,以消除物欲杂念干扰,使其意念诚实。“所谓自欺者,非为此人本不欲为善去恶,但此意随发,常有一念在内阻隔住,不放教表里如一,便是自欺。但当致知,分别善恶了,然后致其谨独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杂,而后意可得其诚也。”③事实上,知行往往是反复多层相互作用互不分离的,没有离行之知,也没有无知之行。常人理解的知,是理论上起辨别是非作用的知,至于行则有专门的领域和方法,不再属于知的范围。朱子对知行本来也有明确划分,对二者关系有“知先行后,知行相须”“先知后行”“知为轻,行为重”等说。朱子也认为格物致知属于知,诚意属于行。但他同时提出的真知说是包含了知行在内的高层次的知。知行善去恶的知是表层的知,真知是深层的表里精粗无不到之知,在意念的层次里面,是否自欺就是因为有两种相反的意念在斗争,故此关键要通过知来区分意念,使得为善去恶的意念占据上风,将意念落于实处。
朱子对“自欺”的注释经过反复修改,自欺可分为两类,有意之欺还是无意之欺,特征是表里不一,知行分离、虚妄不实。具体包括这几种情况:未能纯粹至善,微有差失者;自欺之不觉者,知善恶之分不自觉滑入恶者;自欺之微者,知善恶之分,但又自我苟且自恕者;自欺之尤甚者,外善内恶。
(二)“自欺”之改
修改之一:“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
从本心明知的角度诠释自欺。据陈文蔚《通晦庵先生书问大学诚意章》可知,朱子在己酉前后曾以“心知”解释自欺,认为自欺是“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遮蔽自我本心之光明智慧。陈氏指出朱子此解是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考虑,因知有未穷,故心体有所不明,自欺之意难免发出,造成自我本心的遮蔽。“及观《章句》解自欺之说,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说,初以为疑,反复谛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盖谓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体不明而私意容或窃发,‘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自蔽其心之谓。”①朱子在回信中认为《章句》此解不如前解,过于强调了知的意味,脱离了自欺本意。己酉《答陈才卿》十四,“所喻诚意之说,只旧来所见为是。昨来《章句》却是思索过当,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②。
修改之二:“物欲之私杂乎其间”
甲寅时期从物欲私杂的角度诠释自欺。朱子甲寅年(1194年)给皇帝进讲《大学》所写《经筵讲义》一文,对“自欺”的阐发即由此入手,他说,“人心本善,故其所发亦无不善。但以物欲之私杂乎其间,是以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为自欺耳。能去其欲,则无自欺而意无不诚矣。”①朱子基于人心本善的立场,指出所发意念本来亦皆善。意念之不实源于物欲私念的纷杂惑乱,导致自欺,故消除自欺的工夫在于去除物欲之私。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将意念之善与意念之实等同之,实即善,不实即自欺。也就是把真善统一,妄杂与自欺统一。本来,意念之妄杂应与恶相应,此处与自欺相应,盖朱子认为,自欺有多层次表现,恶则是其中程度最深的一种。故妄杂与自欺相对应,语义更广泛。朱子此时提出消除自欺工夫是“去物欲之私”,立足于理欲、公私的对立,《章句》则认为自欺病根在于知行脱节,立意不同。
从物欲私杂的角度诠释自欺是朱子自欺解尚未成熟定型的表现。朱子在其他著作中亦论及之。《大学或问》即认为,“天下之道,善恶而已”。善为天命天性本心,恶则为物欲所生邪秽之物。人既受制于先天气禀,又为后天私欲所染污,故人性之善受到蒙蔽。“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则善者,天命所赋之本然;恶者,物欲所生之邪秽也。……然既有是形体之累,而又为气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②甲寅年余国秀对此提出疑问,他指出《章句》仅以“物欲”解释自欺、慎独,《或问》则兼用气禀,似有不同。朱子回应二者之别乃详略之分,并无不同。这亦充分证明《章句》在甲寅时期既以物欲之私解释“自欺”。“宋杰尝观传之六章注文释自欺、谨独处,皆以物欲为言。《或问》则兼气禀言之,似为全备。”“此等处不须疑,语意自合有详略处也。”③《语类》亦有“割去物欲之杂”说,如上引李壮祖所记,“但当致知,分别善恶了,然后致其谨独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杂,而后意可得其诚也。”④
修改之三:“若在于善而实则未能(免于)不善也”问:“‘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发若在于善,而实则未能不善也。’‘若’字之义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来一似都善,其实中心有些不爱,此便是自欺。僴。①
从似善而未能纯善的角度诠释。笔者按:此句“未能不善”之说语义颠倒,据下文“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可知“未能”与“不善”之间似夺“免于”二字,当补之。或“不”善之“不”应删去。此处朱子用“若”“实”二字相对,说明从表露在外的行为看来,似乎心之所为皆是为了善,而内在心意却没有做到纯善,夹杂了不纯粹之善,盖其心意非诚也,此即为自欺。此说强调自欺者的表里不一。此一注释相对而言似早,因为在表达表里不一、知行二致义上,后面诸修改较之“若”“实”更鞭辟有力。此处朱子还提及“前日得孙敬甫书”,批评孙氏“自慊”之说有误。
前日得孙敬甫书②,他说“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如此了然后自慊。看经文语意不是如此。“此之谓自慊”,谓“如好好色,恶恶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恶时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与自欺相对,不差豪发。所谓诚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诚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又曰:“自慊则一,自欺则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里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实有些子不愿,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诚伪之所由分也。”僩。③
朱子提出对自慊的理解应把握根本一点:自慊与自欺是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好恶无自欺的当下即是自慊,自慊乃无自欺的自然体现。二者在空间上不共存,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孙氏之误在于割裂了二者对立性,误以为二者之间还存在过渡阶段。朱子指出,诚意与自欺的对立关系亦是如此。自慊与自欺的表现是表里一致还是内外分离,即一心二心,诚伪之分。自慊是纯粹为己之学,是自快足于己也。《文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表明了类似看法,朱子曰:“但如所论,则是不自欺后方能自慊,恐非文意。盖自欺、自慊,两事正相抵背,才不自欺,即其好恶真如好好色,恶恶臭,只为求以自快自足。”①
修改之四:“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
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某意欲改作‘外为善而中实容其不善之杂’,如何?盖所谓‘不善之杂’,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着在这里,此之谓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着在这里,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认错了。只管说个‘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节,缘不奈他何,所以容在这里。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识得他源头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错了。(大概以为有纤豪不善之杂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数,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谓之金,只是欠了分数,如为善有八分欲为,有两分不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这分数。”或云:“如此,则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奈它何底。)荀子曰:‘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某自十六七读时便晓得此意。盖偷心,是不知不觉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则谋,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如公之说,这里面一重不曾透彻在。只是认得个容着,硬遏捺将去。不知得源头工夫在。”……又引《中庸》论诚处而曰,“一则诚,杂则伪”。
“只是一个心,便是诚,才有两个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他彻底只是这一个心,所以谓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间杂,便是两个心。”僴。②
从外善而内心容其不善的角度诠释。朱子师弟所争看来甚小,“未能免”和“容”虽为个别字句之差,牵涉问题却不小。其一,朱子提出“外善内恶”说而不是常用的“阴恶阳善”说,可知此处修改尚早,其根本意思还是强调表里一致。其二,此处纠缠的是知、行、善、恶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敬子的“容于不善之杂”指的是主观上知善而容恶,知行严重脱节者为自欺。如果知行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知善行善或者知恶行恶,或不知善恶而相应行善恶,则不属于自欺。知恶行善又是不可能的,故其实就是知善而行恶这种情况,才是自欺。其三,朱子批评敬子自欺是“知得了善还容着恶”,他认为自欺应该是“知得了不奈何”。敬子之说突出主观上对恶的态度问题,似乎故意纵容恶之存在、发作而不去克制;朱子的“不奈何”说则是表明主观上想去克制但客观上没有能力而导致自欺。二者之别在于自欺到底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所限。朱子认为能力的不足导致容有不善,敬子只是考虑到自欺对恶本来就抱着宽容态度,故批评敬子的“容于不善之杂”说已是第二节,但他对敬子的批评并不切合原意。其实,敬子说更符合自欺之意。朱子“无可奈何”的能力说属于意志行为,是自欺中最高一等。其四,最重要一点在于,朱子认为自欺即是自欠,是“有一豪不快于心”,“微有些没要紧底意思”,后果就是“未能免于不善”,诚意“须是十分真实为善”。他特地引荀子关于心有意识和无意识活动来证明自欺是内心无意识的流动逸出伦理规则之外。朱子反复以分量程度的差别来说明自欺,将判定自欺的标准滑到了是否做到极至,是否达于至善,这偏离了自欺本意的。为了达到这个至善,朱子又反复强调工夫源头格物知至的重要。因为朱子“知”具双重性:真知和半知,但他又没有具体点明,故使其理论看起来充满了矛盾,说自欺是“知得了不奈何”,又强调要从知上(所谓的源头上)做工夫。既然“知得了”,那自然可理解为知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应该到行上、意念上(或如敬子到态度上)去找原因和办法,但朱子还是回到知上。可见所谓“知得了”并非真的知了,而是表面的半知,故还须继续寻求真知。其五,朱子以一心之说判定诚意与自欺之别,再次强调了一心、两心的纯杂关系。一心则自慊,两心则自欺,心不可有间杂。其五,朱子此条自欺诠释已经完全从知行内外分离的角度入手,将自欺的源头推到致知上,放弃了甲寅时期的物欲之私说,表明其自欺解转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伤杂耳。某之言却即说得那个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说得是。盖知其为不善之杂而又盖庇以为之,此方是自欺。……某之说却说高了,移了这位次了,所以人难晓。……今若只恁地说时,便与那‘小人闲居为不善’处都说得贴了。”①
朱子经过一夜反思,承认敬子“容”字说对,抓住了自欺本义,即自欺是对不善虚假行为的有意识的自我纵容,而不是如他所言是无意识的过失,是未能做到极致。如此说方可平顺贴切的解释下文。朱子反思自己的“欠分数说”,“格物致知源头说”说高了,越位了,偏离了“自欺”的本义,造成理解上的晦涩,违反了诠释贴近本文的原则。而且照李敬子之解,方可将下一节文字“小人闲居为不善”贯通。
“次日又曰:夜来说得也未尽,夜来归去又思。看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段,便是连那‘毋自欺也’说。言人之毋自欺时,便要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样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谓如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小人闲居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说‘闲居为不善’,便是恶恶不如恶恶臭;‘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义都贴实平易坦然,无许多屈曲。某旧说忒说阔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样人如旧说者,欲节去之,又可惜,但终非本文之意耳。”②
朱子经过一夜反思,思想有了一大转变,认为应将“毋自欺”和下文“好好色如恶恶臭”连起来说,以声色之生理本能感受来表明道德工夫之真实自然。“斩根”之说与“一于善”相通,强调工夫的决绝有力,彻底干净。下文“小人闲居为不善”一段是作为实例从反面阐发小人的自欺,好善恶恶皆不诚意。如此一来,朱子以“自欺”为中心,打通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四者间的联系,并使得全篇文义贯通无碍,消除了此前割裂理解带来脱离本意的疏阔、高远、艰深之蔽,实践上使学者易于下手用功。“因说诚意章曰:若如旧说,是使初学者无所用其力也。”①
修改之五:“好善阴有不好以相拒,恶恶阴有不恶以相挽”
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里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谓“其好善也,阴有不好者以拒于内;其恶恶也,阴有不恶者,以挽其中。”盖好恶未形时,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恶底藏在里面了。”②朱子还曾用“好善阴有不好”“恶恶阴有不恶”来诠释“小人闲居不善”之内外对立的情形。虽知好善,然内心则阴有不好善之意以拒绝善;虽知恶恶,然内心有不恶之意以挽留恶。此为未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者,在好善恶恶上未能做到表里如一,内外一如,故体现为意念的心理拉锯之战而终不免于自欺者,与敬子所言,“容其不善”,朱子所言“不奈何”相通。此说虽为吕涛己未所记,但应为朱子此前之说,盖《大学或问》已言之,不过《或问》未用“阴”这个词而已,《或问》更强调了真知的重要。“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则其好善也,虽曰好之而未能无不好者以拒之于内。不知恶之真可恶,则其恶恶也,虽曰恶之而未能无不恶者以挽之于中。”③
修改之六:“为恶于隐微之中,诈善于显明之地”
以隐恶显善之说解释“小人闲居为不善”。朱子早在甲寅之《讲义》中即以“为恶于隐微之中,诈善于显明之地”的对比手法,突出小人自欺之甚的特点。小人未能慎独,故于隐微之中行其恶,而在显明之处行其善,其恶为真恶,善为伪诈之善,欺人之善。善、恶,显、微、内、外、虚、实形成一组鲜明对比,尽显小人自欺欺人之情态。《讲义》注:“小人为恶于隐微之中,而诈善于显明之地,则自欺之甚也。”沈僴所录《语类》中,朱子仍提起此说,可见朱子修改之中亦有其一致连贯性。“所谓为恶于隐微之中,而诈善于显明之地,是所谓自欺以欺人也。”①此说朱子随即以阴阳善恶之对比形式取代之,但“诈善”之说《章句》仍保留之,“欲诈为善卒不可诈”。
修改之七:“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与“阳善阴恶,好善恶恶”
“问:诚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旧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发,阳善阴恶,则其好善恶恶,皆为自欺而意不诚矣。’恐初读者不晓。又此句《或问》中己言之,却不如旧注云:‘人莫不知善之当为,然知之不切,则其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故欲诚其意者无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晓。”曰:“不然,本经正文只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说。今若引致知在中间,则相牵不了,却非解经之法。又况经文‘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说话极细。盖言为善之意,稍有不实,照管少有不到处,便为自欺,未便说到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处。若如此则大故无状,有意于恶,非经文之本意也。所谓‘心之所发,阳善阴恶’,乃是见理不实,不知不觉地陷于自欺,非是阴有心于为恶而诈为善以自欺也。”僴。②
朱子此处讨论了诠释视角“致知”与“好善恶恶”。弟子认为“自欺”的今注不如旧注明白易懂,旧注提出,人虽知善之当为,但因非真切之知,故其心所发出之意,必定有阴恶阳善以自欺者。因此诚意工夫在于禁止此阴恶阳善之意的发出。朱子提出三点反驳,一是旧注之解着眼于致知,突出因无真知,故所发之意有阴恶阳善者。而“诚意”章中本无致知之义,将“致知”掺杂于诚意之中,脱离本文原意,侵占了诚意地位,犯有诠释牵合越位之弊。新注符合原文应有之意,与解经当求本意的原则相一致。二是就语义而言,旧、新注语意轻重有别,新注“阳善阴恶,好善恶恶”之说更符合原义。自欺所指意思极为精细,是说人本心存善意,只是在行为、意念上的稍微放松不留神,认识上的“见理不实”,而不自觉的流于自欺,造成表里不一、内外乖张,其本心并非如此。这种自欺的程度很低,是“微有差失”,是“无心之失”,可说是君子之过。旧注“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之说是此人本心即要为恶,而不过以善掩盖而已,这是“存心为恶”,是“大故之恶”,简直是恶人之恶了。如此就语义太重,属于自欺里面最严重的一种,指那种极为明显的大恶。今本所改则相当于最轻微的那种无心而流于自欺者,是从细微无意识处而言,故说工夫极细,这才是原文之意。其三,旧注不当连带下文“小人闲居为不善”来说,“小人闲居为不善”乃是自欺之大者。新注、旧注的主要差别在于从何角度(粗还是细)来理解自欺,朱子的修改趋向于细,认为自欺可能仅仅是君子之过,到小人地步已不是自欺所能概括,已是到了恶的地步,反映出他对于自欺的认识发生了由外在之恶到内在之失的变化。旧新注的另一个差别是,新注没有连“毋”一起说,旧注则牵连一起。在笔墨上,旧注用字50,较今注多出一倍,违背诠释简约精当之原则。从这条讨论亦可看出,朱子自欺诠释从“物欲”转入“致知”后,再次发生变化,转向尽量地切近文本。
朱子此一新注,沈僴于《语类》中还有记载: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发,阳善阴恶,则其好善恶恶,皆为自欺而意不诚矣。”①
此注和旧注相比,删除了“致知”的掺杂,而增强了本章上下文之间的关联,即增加了他在与李敬子讨论时提出的“自欺”应与下文“好善恶恶”相关联的看法,此注与《章句》相比,仍有不少差异处。其一,因为在“毋自欺中”并无“阳善阴恶”之意,考虑到与原文本意的和谐,故《章句》将“阳善阴恶”之说移到了下一节“小人见君子而后厌然”的注释中,以此专指小人之自欺,即程度严重之自欺。“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其二,《章句》突出了知、意脱节的问题,强调了诚意工夫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同时仍保留了致知与自欺的紧密关联,“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此是对旧注“人莫不知善之当为”的回归,此处新注“阳善阴恶”仅反映出表里不一致,没有强调知在诚意中的先决性作用,未能从根源上指出自欺的病因。其三,《章句》和旧注的共同点在于皆表明自欺是就一己之隐微意念而言,是个人私下的个体性活动,自欺是知行分离,这种分离在程度上极为轻微。其四,《章句》诠释更为精练。
修改之八:“则无待于自欺而意无不诚也”
又问:“今改注下文云:‘则无待于自欺而意无不诚也’,据经文方说‘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辞’,若说‘无待于自欺’,恐语意太快,未易到此。”僴。①
此句注释不见于《章句》,已删之。弟子认为“无待于自欺”的说法在语义上伤快,与经文“毋(禁止)自欺”之义不合。朱子的辩解是,既然能够禁止不自欺,说明已经能知理之是非,自觉行好善恶恶工夫,使意念之发纯善无恶,由此即可达到不自欺,“毋自欺”虽有禁止义,但不自欺之状态,并非勉强控制所能达到。朱子以人受寒病肚子为譬,说明知上分晓善恶在工夫上的重要。其实朱子之说并不合原意,工夫是无限反复的过程,不可以说不做禁止自欺的工夫。再就经文意思来看,毋自欺和无待自欺是有差距的,从“无待自欺”看不出工夫,而只是工夫达到后的一种境界、效用罢了。
修改之九:“假托”还是“掩覆”
国秀问:“《大学》诚意,看来有三样。一则内全无好善恶恶之实,而专事掩覆于外者,此不诚之尤也;一则虽知好善恶恶之为是,而隐微之际,又苟且以自瞒底;一则知有未至,随意应事,而自不觉陷于自欺底。”曰:“这个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浅之不同耳。”焘。
次早云:“夜来国秀说自欺有三样底,后来思之,是有这三样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浅深之不同。”又因论以“假托”换“掩覆”字云:‘假托’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轻,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论诚与不诚不特见之于外,只里面一念之发,便有诚伪之分。”①
余国秀提出不诚自欺有三种情况:其一,自欺之尤者,专事掩覆于外,完全无丝毫行善去恶之实;其二,自欺之微者,知善恶之分,但隐微之际又苟且自恕,意有不诚者;其三,自欺之不觉者,受知识所限,未能分辨善恶而不自觉滑入自欺者。朱子开始认为不需要做此分别,三者性质皆同,都是自欺,只是情况有深浅之别。后来反思确实存在这三种情况,但又指出皆是同一性质下的浅深之别。朱子又和余国秀讨论用“假托”还是“掩覆”描述“自欺”,二者形容自欺形状,畸轻畸重,难得恰好。此两字今本皆不用。朱子对自欺之类型亦略有分别,如他指出自欺的表现:内外分离,表现为为人之学,与为己相对;有始无终懈怠之学,与自始至终的彻底连续性不同;九分善,一分苟且之学,缺乏纯粹性。诚意之学则应表里如一,内外彻底,纤毫不违,为己不苟。“凡恶恶之不实,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实不然,或有所为而为之,或始勤而终怠,或九分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实而自欺之患也。所谓诚其意者,表里内外彻底皆如此,无纤豪丝发苟且为人之弊。”②
据以上修改历程可知,朱子在围绕自欺的多次修改中,认识有很大变化,己酉年曾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说,突出了致知对于诚意的重要性;甲寅时期侧重“物欲之私”解释,着眼天理人欲的分裂;此后转向知行背离、内外对立、阴阳割裂的角度诠释,期间很注意把握致知与诚意、自欺之程度等问题,屡有调整。丙辰至戊午年间提出“若在于善而实则未能”说,以“若、实”表明内外的背离,后又改为“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此一“中外善恶”的“纯杂”背离说有一定代表性。此后朱子又先后提出“阴阳善恶”说,前一次从致知说自欺,认为“知之不切”导致“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此种“阴恶阳善”者乃有意为恶,为自欺中最严重者。后一次修改去除了“知之不切”,提出“阳善阴恶”说,认为自欺是无心之过,为自欺中最轻微者,而且以至善的要求来看待自欺与否,将自欺认定为“自欠”,是知上有丝毫未尽所造成的,“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处”,便是自欺,这拔高了对自欺的认识。阴阳善恶说在朱子自欺说中也颇具代表性。此后,朱子还提出“无待于自欺而意无不诚”说,此说亦过于强调知的意义,且与本文“毋”的禁止意有所背离。到去世前一年的己未年,朱子还在讨论自欺之类别,探讨用“假托”还是“掩覆”解释自欺,文中有“掩其不善”说,朱子最终倾向用“掩”字,《章句》即用了“掩”和“诈”的对说。
据朱子对自欺的繁复修改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即朱子诚意之解的根本线索是意念之善与恶的关系。无论哪一次修改,总是围绕善与恶展开。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胡炳文等提出的“一于善”说更符合朱子本章修改之历程,它揭示了诚意的根本特质。朱子颇为重视的《大学或问》亦是着力阐发善恶,开篇即点出本章之旨围绕善恶展开,“天下之道,善恶而已”。诚意章最后以“故君子必诚其意”重复之说结束全章,《章句》之解,仍然落实于意念之善,“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结之”①。《语类》指出诚意最紧要,紧要处在于诚意乃是分别善恶关节处,故最要用力。“要紧最是诚意时节,正是分别善恶,最要着力。”②“一于善”说正是鲜明的揭示诚意归于善的根本特色。
(三)自慊与自欺
反观朱子对“自慊”的认识,虽有提及,但并非核心问题。朱子长期以来,仅注重“自慊”的个别意义,并未将之与诚意、自欺之解相联系。直到《经筵讲义》之时,仍只是将之与“毋自欺”相连。过了几年,朱子方才意识到应该将“自慊”“慎独”与“自欺”一起,纳入诚意的体系中。《经筵讲义》将诚意章第一部分切分为二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为第一层,于“毋自欺”后断开随文解释;“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为第二层,而且“自慊”与“慎独”亦未关联解释,各自独立一句。①今本《章句》则从开头“所谓”一直到“慎其独”连起来讲,《讲义》断开为二,表明朱子此时没有认识到诚意包含自欺、自慊、慎独三个要点,将它们前后割裂,对诚意的阐发缺少一种有力例证和说明,而且在文势上也不连贯。朱子戊午《答孙敬甫》一书,仍未以“自欺”将诸概念串联起来。如他认为,诚意即是不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说明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则为单独一节。“故其文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继之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实。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谓自慊,即是言如恶恶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谓必如此而后能自慊也。所论谨独一节,亦似太说开了。”②上文“自欺”修改四所引《语类》反映出朱子去世前一两年在与李敬子反复讨论自欺修改中,方才反思应将自慊、慎独纳入诚意范围下。
比较《讲义》、《或问》、《章句》,对自慊、慎独之解并无差别,差别在于自欺,《讲义》侧重好恶深切,意常快足而无自欺。即自慊而无自欺,即陈栎所主张的“必自慊而无自欺”。
《讲义》:“臣熹曰:如恶恶臭,恶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之地也。好善恶恶深切如此,则是意常快足而无自欺矣。”③
《章句》:“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①
《章句》加大了“自欺”的阐发,首先即指出诚意是自修之事,“致知”对于诚意自修具有不可或缺的先在性,必须在知上分别善恶,方能在行上用力。诚意独立于致知的意义在于,光有致知是不够的,必须落实于自身的切己行动,此一行动要求真诚向内,坚决果敢,彻底为己,而自慊是包含于其中的一个效验,不具有工夫意义。《章句》与《讲义》的差别在于,《章句》深入细致剖析了诚意毋自欺的工夫,即阐明了诚意工夫的理论前提、实际操作、必然效用。《讲义》“意常快足而无自欺”之类的说法仅仅侧重诚意之效用,过于轻快,亦使学者无所用力。故此类说法《章句》均不见之。
与耗尽心力诠释“自欺”相反,朱子有意删除了《章句》有关“自慊”之解。如朱子对《或问》此章的修改,即删除了此前所引的程子自慊之说,认为程子之说过头了。问:“《或问》‘诚意’章末,旧引程子自慊之说,今何除之?”曰:“此言说得亦过。”②程子之说为,“人须知自慊之道,自慊者,无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则张子厚所谓‘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程子认为自慊则无不足,自然无自欺了,引张载说指出若有不足,则表明心仍在外,杂念私欲未尽,故意未诚,心未专一也。朱子反思此说过高,拔高了自慊的意义。而据曾祖道丁巳(1197年)所记《语类》,朱子尚将自慊理解为无不足,并引横渠之说为证,由此可知陈淳所记上条,乃是己未所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慊者,无不足也。如有心为善,更别有一分心在主张他事,即是横渠所谓‘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③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