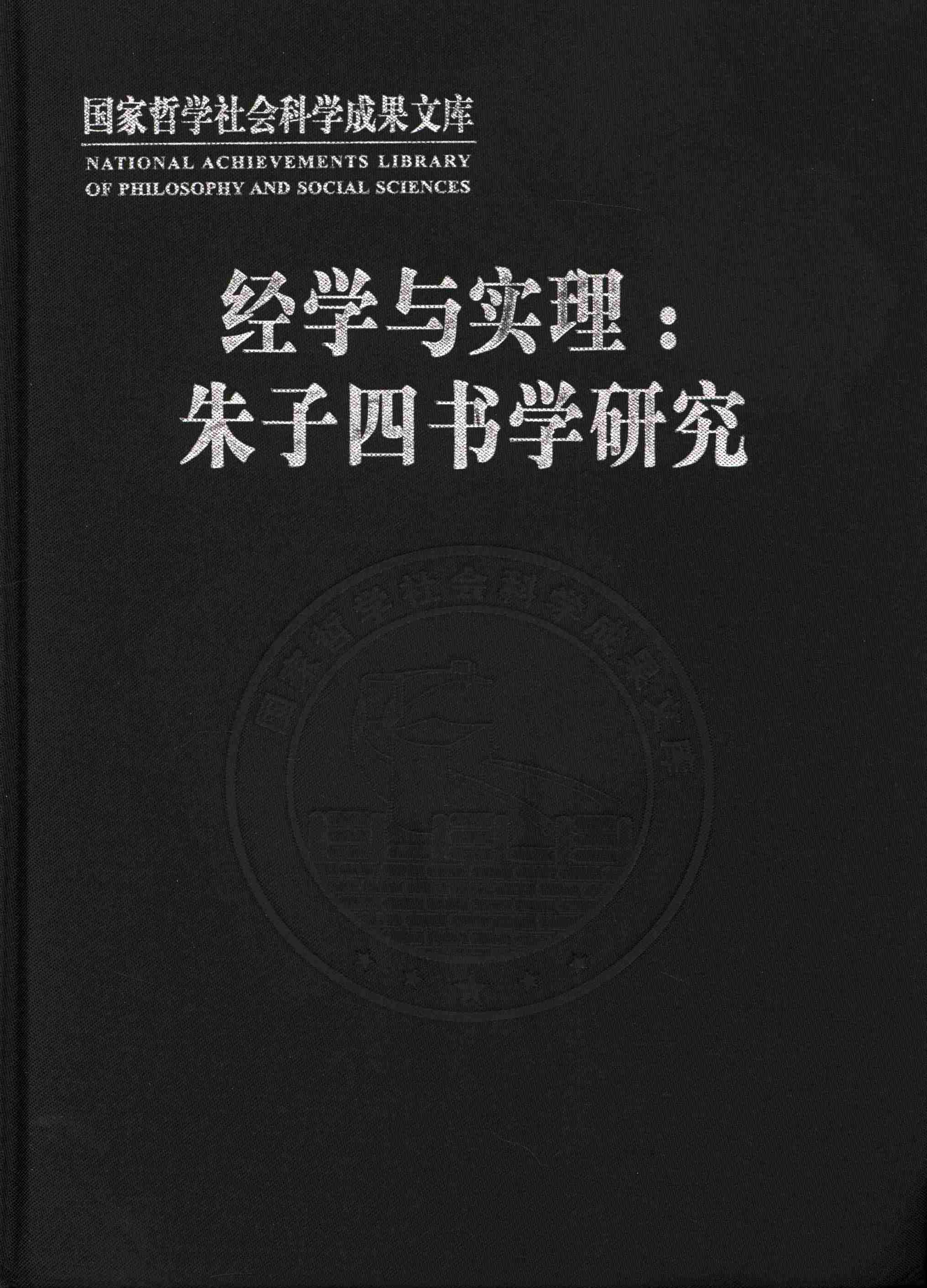三 “知言,本也;养气,助也”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80 |
| 颗粒名称: | 三 “知言,本也;养气,助也”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 |
| 页码: | 221-228 |
| 摘要: | 本文章主要讨论了朱子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独特阐发和理解。朱子认为,知言是知心之理,为养气之本,养气是知言之末,此序不容改变颠倒。养气以直养而无害为根本,以配义、集义为根本的配养。浩然之气是气无亏欠时的形态,气之充盈无亏欠其实即是人心之无亏欠。若能于工夫上做到自反而直,使所行所思皆符合道义,无所亏欠,那么就养护了此气。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养气之前提——知言。孟子自言不动心的长处在两个方面,“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朱子站在理学的立场,以格物穷理、知先行后、主次本末等理论对知言及与养气关系作了独特阐发。朱子对知言给予了极高重视,视为此章主旨,“此一章专以知言为主”②。他以《大学》格物穷理解释知言,认为“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③。“尽心知性”在朱子看来就是经过格物穷理后所获得的物格知至,“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④达此,则于天下之事理无所不通,于是非得失之根源无所不得,故知言也就是知理、知道。朱子引用程子观点,提出辨别是非的前提在于心通达于道,以道裁断是非,正如用称重仪器之权衡物体之也。这即是孟子知言之意,是从道的高度来辨别言之是非。“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⑤
朱子从知行关系来理解知言和养气的关联。他指出,知和理,行和事分别相对应,知言以明夫道义,达到于天下事了然无疑之地步;养气以辅佐配合道义,达到行天下事无所畏惧的地步。知言明理故无疑,养气配义故无惧,正因为知行理事上的双向并进,相互作用,孟子才能担当起大任而不动心。在知行关系上,朱子主张知先行后。据此,则知言在养气之前,为养气之前提,“须是先知言。知言,则义精而理明,所以能养浩然之气。”①
朱子还以理气本末说来判定知言和养气的关系,知言是知心之理,此理对气有主宰作用,为气之本,气则是理之辅助,是理之卒徒。故知言是养气之本,养气是知言之末,此序不容改变颠倒。“盖知言只是知理。……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②
养气之根本——直养、配义、集义。
以直养而无害。孟子在感叹浩然之气“难言也”后,还对此气做了阐发,引起了后世的纷争。第一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对这句话理解的分歧首先就表现在断句上,小程子据《周易》“直方大”说,提出将“直”断在上半句,与“大、刚”并列为描述气之特点的词,亦正好与《易》说相合。朱子以前后文势和文义为根据,认为当在“刚”字后断开,“直”字放在后半句,并从文势、文义和诠释的角度批评程子说。
据文势,若按程子说,孟子当用“至直”而不是“以直”,“文势当如此说。若以‘直’字为句,当言‘至大至刚至直’。”再则,“直”字若归属上句,则和“刚”义重复;若属下句,则前后贯通而无此弊。故朱子宁愿取俗师之说而舍赵岐、程子说。“今以‘直’字属上句,则与‘刚’字语意重复,徒为赘剩而无他发明;若以‘直’字属之下句,则既无此病而与上文‘自反而缩’之意,首尾相应,脉络贯通,是以宁舍赵、程而从俗师之说。”③据上下文义,上文和下文皆有“直”义,与“直养”正好相应,这样才符合圣贤之言首尾呼应之义。“又此章前后相应,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缩’,后言‘配义与道’。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乃‘自反而缩’之意。”①据所指关系,和“至大至刚”描述气体不同,“以直”乃是对养气工夫之描述。针对伊川从义理上嫌“直养”说有以物养物之义,朱子认为“直养”并不是物物相养,“直”是自反而直,是用功处,“养”则是维持呵护此浩然之气,若没有此“直养”工夫,仅说“养而无害”,就没有突出养的内容和主宰,无法形成浩然之气。且在语义上也显得软瘫,没有刚硬气魄,与全段风格不相符合,与孟子刚勇性格不相匹配。“故知‘以直’字属下句,不是言气体,正是说用工处。若只作‘养而无害’,却似秃笔写字,其话没头。观此语脉自前章‘缩、不缩’来,下章又云‘是集义所生’,义亦是直意”②。根据诠释方法,看文字当从本文入手,顺原文语脉,求圣贤原义,不可牵扯他说,程子以《周易》来断定《孟子》的做法有牵扯之弊,《孟子》说和《易说》自有差别,“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将《孟子》自看,便见《孟子》说得甚粗,《易》却说得细”。③朱子进一步指出小程子坚持否定大程子的“以直养”说正反映出其本人性格之固执。
朱子主张如此理解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上文曾子提出“自反而缩”。朱子以《礼记》为证,说明“缩就是直。”以直养就是自反而缩之意,“惟其自反而缩,则得其所养。”曾子不动心在于反求诸己而所为正直,由此产生出行动的勇气,和以正直保养护持此浩然之气相应。“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乃‘自反而缩’之意。”④朱子还指出诸说虽有断句相同者,但并不可取,因为他们“所以为说者,不本于自反而缩之云,则非孟子之意矣”⑤。朱子引用谢上蔡的观点指出,“浩然之气,须于心得其正时识取。”⑥浩气本源自义理,当行正直正义之事时方能体认保持。浩然仅仅是气无亏欠时的形态,气之充盈无亏欠其实即是人心之无亏欠。故气之状态如何完全取决于人心,若能于工夫上做到自反而直,使所行所思皆符合道义,无所亏欠,那么就养护了此气,这样养气就与人生有了直接的关联。同样,对浩然之气的最大伤害就是个人之私意。一旦为私意所遮蔽,则此气就会软瘫下来,顿然失其刚硬至大状态,而变得极其小弱也。朱子引用程子的观点说,“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却甚小也。”①
配义与道。孟子描述浩然之气的第二句是:“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句话同样引起后世纷争。朱子依然从文义训诂入手,对之作出了新的诠释。首先,朱子将“配”解释为“合而有助”,突出道义与气的相互推动,体现出朱子的创造性。朱子之前如程子等将“配”释为“合”,“配者,合也。”朱子增加了“助”字,意在强调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问‘合而有助’之意。曰:若无气以配之,则道义无助”②。朱子还分别以天理、人心解释道、义,“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③
其次,朱子指出,道义与气是相互推动关系。气与道义相合形成浩然之气,此气反过来有助于道义的推行,二者“是两相助底意。”故“初下工夫时,便自集义,然后生那浩然之气。及气已养成,又却助道义而行”④。先集义以养成此浩然之气,此浩气与道义相吻合,就能推动道义,使人的行为自信无畏,坦诚果敢,没有疑惧。朱子特别强调了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他肯认人性先天皆善,皆愿行善,然而往往不能坚决行之,一贯行之,见义而不能勇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作为行义推动力的勇气,缺少一种弘毅精神。故在行道上就表现为不彻底、不连续(具有间断性、随意性),最终造成人的道德素养无法提升,成为“一个衰底人”。“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⑤
再次,朱子以理气之说对道义与气的关系做了深入剖析。朱子从理气不离、理先气后的角度阐述道义与气为形上、形下的本末先后关系,创生与支撑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分亦不合的一体关系。先有道义然后产生浩气,但道义是空虚无形不可视听之物,自身并无力量,它的实行必须得到浩气的支撑才能呈现作为。一般人亦有行善而合乎道义者,然而必须有这个气作为动力,人的道义才能树立起来。“(道、义)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气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以人言之,则必明道集义,然后能生浩然之气,而义与道也,又因是气而后得以行焉。”①他肯定“气与道义只是一滚发出来”②的一体不分关系,同时亦保持各自的形上形下界限,“气与义自是二物。”道义是公共的形上之体,气则是自家私有形下之物,二者又是普遍公共与个体私有关系,道义本自无情,自家之气合下即有,故应善自保养浩气,并以之助养道义;若不加以存养,则道义和气就两不相干了。“道义是公共无形影底物事,气是自家身上底物。道义无情,若自家无这气,则道义自道义,气自气,如何能助得他?”③
朱子对“无是,馁也”的理解引起学者纷争,关键在于“是”指代的是道义还是浩气。朱子与二程一致,认为“是”指浩气,“馁”的主体是道义。但很多学者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的理由是:道义作为天地之理,亘古长存,怎么会馁呢?只有气才会馁。故本句话当理解为“没有道义的支持,气就会馁下来。”朱子好友吕子约即持此解,吕氏认为“道义本存乎血气,但无道义则此气便馁而止为血气之私,故必配义与道,然后能浩然而无馁乎”④。朱子从两点展开驳斥:一是理解此章的关键在于分清主宾关系。孟子此处的主旨是强调浩然之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故当以浩气为主,道义为辅。“孟子答公孙丑问气一节,专以浩然之气为主。”朱子判读的根据是孟子两句皆是以“其为气也”为话头,语义上皆以浩气为主,故当突出气。其二,从文本诠释来讲,若如吕说,则“语势不顺,添字太多。”因为孟子“且其上既言‘其为气也’以发语,而其下复言‘无是馁也’以承之,则所谓‘是’者固指此气而言。”而且吕说造成上下三句语意重复,于文势、文义和孟子这位圣贤的言语风格皆不合。“今乃连排三句只是一意,都无向背彼此之势,则已甚重复而太繁冗矣。”①
集义。孟子接下来对“浩然之气”的阐发转到义上,说该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此句同样引起后世纷说。朱子认为,集义就是积善,是积集善行,以义裁断事理、使事事合乎宜,不是取乎彼而集之于此也。“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②朱子特别强调集义行善的自然性、长期性、内在性、彻底性、普遍性,将之视为内在生命持久一贯的自由行动。它与袭义的差别也就在于此,袭义只是偶尔的掩袭于义,仅仅是一种外在生命的行为,本非己有。“集义是岁月之功,袭取是一朝一夕之事。从而掩取,终非己有也。”③
朱子强调集义是养气工夫之紧要所在。浩气最初之养成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行事是否皆合乎道义。只有时时行道,事事合宜,内心自我反思而心中无所愧疚亏欠时,浩气才会自然而然地由衷产生,此气内在根植于个人心中,并非偶尔行一道义之举就可从外偷袭而得。“而其养之之始,乃由事皆合义,自反常直,是以无所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④朱子认为集义给心灵带来了俯仰无愧的满足感愉悦感,内心是否有此自慊之感,是判定拥有浩然之气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自慊又取决于行为是否合乎道义,倘若做了不合道义之事,哪怕仅有一次,在进行内心反省时,必然会产生不安,不快足,此气则会顿然软瘫,全身感受到虚欠空虚。“言所行一有不合于义,而自反不直,则不足于心而其体有所不充矣。”⑤
进而朱子断定这已经足以说明义在内而非外,告子与孟子的差别在于,他坚持义外说,认为人心乃是一块“白板”,义无关乎人心。故在工夫上不顾行为之合宜与否,仅仅是强制其心而不动,如此必定无法产生浩然之气。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所犯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义外说,不知言虽在外,而理则在内也。“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内义外,而不复以义为事,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矣。上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外义之意。”①朱子转而批评陆学为“袭义”说,指出告子摒义于外,强制本心的做法,和陆象山静坐不读书相近。陆氏门徒包显道等认为,只要一事上做得合乎道义,便可由此提升精神境界,朱子指出这就是告子的袭义说。因为“盖义本于心,不自外至。积集此义而生此气,则此气实生于中”②。陆象山则认为在书上讲求义理,放弃对心的用功,才是告子义外之义。据此亦见出朱陆之学在为学之方上存在主内主外趋向的不同。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是养气中一节目③
孟子提出集义还须做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对于此句的理解亦存在差异。首先在文本断句上存在两种看法,分歧在于是否将“正心”放在一起,伊川和明道各持一说。朱子主张二者皆可,但为了避免与《大学》“正心”相重,故将“正”字属上。朱子以《春秋》为根据,将“正”解释为“预期、等待”,强调其义和《大学》“正心”之“正”意不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连上句亦得。但避《大学》‘正心’字,故将‘心’字连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义。”④朱子指出“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长”仅仅是是养气工夫的一个环节,是对养气工夫的一种限定节制,并非养气工夫之根本,只是“涵泳底意思”,它们与养气本来并无关系,“四者初无与养气事。”只是孟子用之于此大致描述工夫之界限范围而已,是一种补充,批评学者对此过于重视没有抓住根本。“今人说养气,皆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四句上。要紧未必在此。药头只在那‘以直养而无害’及‘集义’上。这四句却是个炮炙锻炼之法。”①
朱子对“事正忘助”工夫进行分析。必有事之事即是养气以集义为事,假如此气未达到充盈饱满状态,则应保持勿忘其事的态度,同时亦不可妄有所作为以助其长,当顺其自然,这是集义养气的自然节度。告子强制其心,必然有“正”“助”之病也。“事正忘助”四者相互作用,有事、勿忘是集义工夫,勿正、勿助长是气之本体的工夫,对本体不可有期待之心、不可有用力添助之举。既要坚持集义的事上用力工夫,也要保持维护本体自然的克制之工。“事、正、忘、助相因。无所事,必忘;正,必助长。”②“必有事”即是全部工夫所在,“勿正、勿忘、勿助长”本是辅助,起对此工夫的限制作用,使之不要犯下这正、忘、助长的错误。正是因为有了这三句的限制,才促使人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保持意志清醒,于此限制中达到对本体的透悟而获得一种自由。本体随时遍在,于万物上皆可显现,无须外求。由此见出儒佛之别,吾儒与佛老之别在于洞见本体后,还要在事上下工夫,还须遵从原有外在规矩限制,只不过这种遵从已经达到浑然不觉地步而已。
朱子从知行关系来理解知言和养气的关联。他指出,知和理,行和事分别相对应,知言以明夫道义,达到于天下事了然无疑之地步;养气以辅佐配合道义,达到行天下事无所畏惧的地步。知言明理故无疑,养气配义故无惧,正因为知行理事上的双向并进,相互作用,孟子才能担当起大任而不动心。在知行关系上,朱子主张知先行后。据此,则知言在养气之前,为养气之前提,“须是先知言。知言,则义精而理明,所以能养浩然之气。”①
朱子还以理气本末说来判定知言和养气的关系,知言是知心之理,此理对气有主宰作用,为气之本,气则是理之辅助,是理之卒徒。故知言是养气之本,养气是知言之末,此序不容改变颠倒。“盖知言只是知理。……盖知言,本也;养气,助也。”②
养气之根本——直养、配义、集义。
以直养而无害。孟子在感叹浩然之气“难言也”后,还对此气做了阐发,引起了后世的纷争。第一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对这句话理解的分歧首先就表现在断句上,小程子据《周易》“直方大”说,提出将“直”断在上半句,与“大、刚”并列为描述气之特点的词,亦正好与《易》说相合。朱子以前后文势和文义为根据,认为当在“刚”字后断开,“直”字放在后半句,并从文势、文义和诠释的角度批评程子说。
据文势,若按程子说,孟子当用“至直”而不是“以直”,“文势当如此说。若以‘直’字为句,当言‘至大至刚至直’。”再则,“直”字若归属上句,则和“刚”义重复;若属下句,则前后贯通而无此弊。故朱子宁愿取俗师之说而舍赵岐、程子说。“今以‘直’字属上句,则与‘刚’字语意重复,徒为赘剩而无他发明;若以‘直’字属之下句,则既无此病而与上文‘自反而缩’之意,首尾相应,脉络贯通,是以宁舍赵、程而从俗师之说。”③据上下文义,上文和下文皆有“直”义,与“直养”正好相应,这样才符合圣贤之言首尾呼应之义。“又此章前后相应,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缩’,后言‘配义与道’。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乃‘自反而缩’之意。”①据所指关系,和“至大至刚”描述气体不同,“以直”乃是对养气工夫之描述。针对伊川从义理上嫌“直养”说有以物养物之义,朱子认为“直养”并不是物物相养,“直”是自反而直,是用功处,“养”则是维持呵护此浩然之气,若没有此“直养”工夫,仅说“养而无害”,就没有突出养的内容和主宰,无法形成浩然之气。且在语义上也显得软瘫,没有刚硬气魄,与全段风格不相符合,与孟子刚勇性格不相匹配。“故知‘以直’字属下句,不是言气体,正是说用工处。若只作‘养而无害’,却似秃笔写字,其话没头。观此语脉自前章‘缩、不缩’来,下章又云‘是集义所生’,义亦是直意”②。根据诠释方法,看文字当从本文入手,顺原文语脉,求圣贤原义,不可牵扯他说,程子以《周易》来断定《孟子》的做法有牵扯之弊,《孟子》说和《易说》自有差别,“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将《孟子》自看,便见《孟子》说得甚粗,《易》却说得细”。③朱子进一步指出小程子坚持否定大程子的“以直养”说正反映出其本人性格之固执。
朱子主张如此理解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上文曾子提出“自反而缩”。朱子以《礼记》为证,说明“缩就是直。”以直养就是自反而缩之意,“惟其自反而缩,则得其所养。”曾子不动心在于反求诸己而所为正直,由此产生出行动的勇气,和以正直保养护持此浩然之气相应。“所谓‘以直养而无害’,乃‘自反而缩’之意。”④朱子还指出诸说虽有断句相同者,但并不可取,因为他们“所以为说者,不本于自反而缩之云,则非孟子之意矣”⑤。朱子引用谢上蔡的观点指出,“浩然之气,须于心得其正时识取。”⑥浩气本源自义理,当行正直正义之事时方能体认保持。浩然仅仅是气无亏欠时的形态,气之充盈无亏欠其实即是人心之无亏欠。故气之状态如何完全取决于人心,若能于工夫上做到自反而直,使所行所思皆符合道义,无所亏欠,那么就养护了此气,这样养气就与人生有了直接的关联。同样,对浩然之气的最大伤害就是个人之私意。一旦为私意所遮蔽,则此气就会软瘫下来,顿然失其刚硬至大状态,而变得极其小弱也。朱子引用程子的观点说,“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却甚小也。”①
配义与道。孟子描述浩然之气的第二句是:“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句话同样引起后世纷争。朱子依然从文义训诂入手,对之作出了新的诠释。首先,朱子将“配”解释为“合而有助”,突出道义与气的相互推动,体现出朱子的创造性。朱子之前如程子等将“配”释为“合”,“配者,合也。”朱子增加了“助”字,意在强调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问‘合而有助’之意。曰:若无气以配之,则道义无助”②。朱子还分别以天理、人心解释道、义,“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③
其次,朱子指出,道义与气是相互推动关系。气与道义相合形成浩然之气,此气反过来有助于道义的推行,二者“是两相助底意。”故“初下工夫时,便自集义,然后生那浩然之气。及气已养成,又却助道义而行”④。先集义以养成此浩然之气,此浩气与道义相吻合,就能推动道义,使人的行为自信无畏,坦诚果敢,没有疑惧。朱子特别强调了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他肯认人性先天皆善,皆愿行善,然而往往不能坚决行之,一贯行之,见义而不能勇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作为行义推动力的勇气,缺少一种弘毅精神。故在行道上就表现为不彻底、不连续(具有间断性、随意性),最终造成人的道德素养无法提升,成为“一个衰底人”。“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⑤
再次,朱子以理气之说对道义与气的关系做了深入剖析。朱子从理气不离、理先气后的角度阐述道义与气为形上、形下的本末先后关系,创生与支撑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分亦不合的一体关系。先有道义然后产生浩气,但道义是空虚无形不可视听之物,自身并无力量,它的实行必须得到浩气的支撑才能呈现作为。一般人亦有行善而合乎道义者,然而必须有这个气作为动力,人的道义才能树立起来。“(道、义)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气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以人言之,则必明道集义,然后能生浩然之气,而义与道也,又因是气而后得以行焉。”①他肯定“气与道义只是一滚发出来”②的一体不分关系,同时亦保持各自的形上形下界限,“气与义自是二物。”道义是公共的形上之体,气则是自家私有形下之物,二者又是普遍公共与个体私有关系,道义本自无情,自家之气合下即有,故应善自保养浩气,并以之助养道义;若不加以存养,则道义和气就两不相干了。“道义是公共无形影底物事,气是自家身上底物。道义无情,若自家无这气,则道义自道义,气自气,如何能助得他?”③
朱子对“无是,馁也”的理解引起学者纷争,关键在于“是”指代的是道义还是浩气。朱子与二程一致,认为“是”指浩气,“馁”的主体是道义。但很多学者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的理由是:道义作为天地之理,亘古长存,怎么会馁呢?只有气才会馁。故本句话当理解为“没有道义的支持,气就会馁下来。”朱子好友吕子约即持此解,吕氏认为“道义本存乎血气,但无道义则此气便馁而止为血气之私,故必配义与道,然后能浩然而无馁乎”④。朱子从两点展开驳斥:一是理解此章的关键在于分清主宾关系。孟子此处的主旨是强调浩然之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故当以浩气为主,道义为辅。“孟子答公孙丑问气一节,专以浩然之气为主。”朱子判读的根据是孟子两句皆是以“其为气也”为话头,语义上皆以浩气为主,故当突出气。其二,从文本诠释来讲,若如吕说,则“语势不顺,添字太多。”因为孟子“且其上既言‘其为气也’以发语,而其下复言‘无是馁也’以承之,则所谓‘是’者固指此气而言。”而且吕说造成上下三句语意重复,于文势、文义和孟子这位圣贤的言语风格皆不合。“今乃连排三句只是一意,都无向背彼此之势,则已甚重复而太繁冗矣。”①
集义。孟子接下来对“浩然之气”的阐发转到义上,说该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此句同样引起后世纷说。朱子认为,集义就是积善,是积集善行,以义裁断事理、使事事合乎宜,不是取乎彼而集之于此也。“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②朱子特别强调集义行善的自然性、长期性、内在性、彻底性、普遍性,将之视为内在生命持久一贯的自由行动。它与袭义的差别也就在于此,袭义只是偶尔的掩袭于义,仅仅是一种外在生命的行为,本非己有。“集义是岁月之功,袭取是一朝一夕之事。从而掩取,终非己有也。”③
朱子强调集义是养气工夫之紧要所在。浩气最初之养成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行事是否皆合乎道义。只有时时行道,事事合宜,内心自我反思而心中无所愧疚亏欠时,浩气才会自然而然地由衷产生,此气内在根植于个人心中,并非偶尔行一道义之举就可从外偷袭而得。“而其养之之始,乃由事皆合义,自反常直,是以无所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④朱子认为集义给心灵带来了俯仰无愧的满足感愉悦感,内心是否有此自慊之感,是判定拥有浩然之气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自慊又取决于行为是否合乎道义,倘若做了不合道义之事,哪怕仅有一次,在进行内心反省时,必然会产生不安,不快足,此气则会顿然软瘫,全身感受到虚欠空虚。“言所行一有不合于义,而自反不直,则不足于心而其体有所不充矣。”⑤
进而朱子断定这已经足以说明义在内而非外,告子与孟子的差别在于,他坚持义外说,认为人心乃是一块“白板”,义无关乎人心。故在工夫上不顾行为之合宜与否,仅仅是强制其心而不动,如此必定无法产生浩然之气。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所犯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义外说,不知言虽在外,而理则在内也。“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内义外,而不复以义为事,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矣。上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外义之意。”①朱子转而批评陆学为“袭义”说,指出告子摒义于外,强制本心的做法,和陆象山静坐不读书相近。陆氏门徒包显道等认为,只要一事上做得合乎道义,便可由此提升精神境界,朱子指出这就是告子的袭义说。因为“盖义本于心,不自外至。积集此义而生此气,则此气实生于中”②。陆象山则认为在书上讲求义理,放弃对心的用功,才是告子义外之义。据此亦见出朱陆之学在为学之方上存在主内主外趋向的不同。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是养气中一节目③
孟子提出集义还须做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对于此句的理解亦存在差异。首先在文本断句上存在两种看法,分歧在于是否将“正心”放在一起,伊川和明道各持一说。朱子主张二者皆可,但为了避免与《大学》“正心”相重,故将“正”字属上。朱子以《春秋》为根据,将“正”解释为“预期、等待”,强调其义和《大学》“正心”之“正”意不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连上句亦得。但避《大学》‘正心’字,故将‘心’字连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义。”④朱子指出“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长”仅仅是是养气工夫的一个环节,是对养气工夫的一种限定节制,并非养气工夫之根本,只是“涵泳底意思”,它们与养气本来并无关系,“四者初无与养气事。”只是孟子用之于此大致描述工夫之界限范围而已,是一种补充,批评学者对此过于重视没有抓住根本。“今人说养气,皆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四句上。要紧未必在此。药头只在那‘以直养而无害’及‘集义’上。这四句却是个炮炙锻炼之法。”①
朱子对“事正忘助”工夫进行分析。必有事之事即是养气以集义为事,假如此气未达到充盈饱满状态,则应保持勿忘其事的态度,同时亦不可妄有所作为以助其长,当顺其自然,这是集义养气的自然节度。告子强制其心,必然有“正”“助”之病也。“事正忘助”四者相互作用,有事、勿忘是集义工夫,勿正、勿助长是气之本体的工夫,对本体不可有期待之心、不可有用力添助之举。既要坚持集义的事上用力工夫,也要保持维护本体自然的克制之工。“事、正、忘、助相因。无所事,必忘;正,必助长。”②“必有事”即是全部工夫所在,“勿正、勿忘、勿助长”本是辅助,起对此工夫的限制作用,使之不要犯下这正、忘、助长的错误。正是因为有了这三句的限制,才促使人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保持意志清醒,于此限制中达到对本体的透悟而获得一种自由。本体随时遍在,于万物上皆可显现,无须外求。由此见出儒佛之别,吾儒与佛老之别在于洞见本体后,还要在事上下工夫,还须遵从原有外在规矩限制,只不过这种遵从已经达到浑然不觉地步而已。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