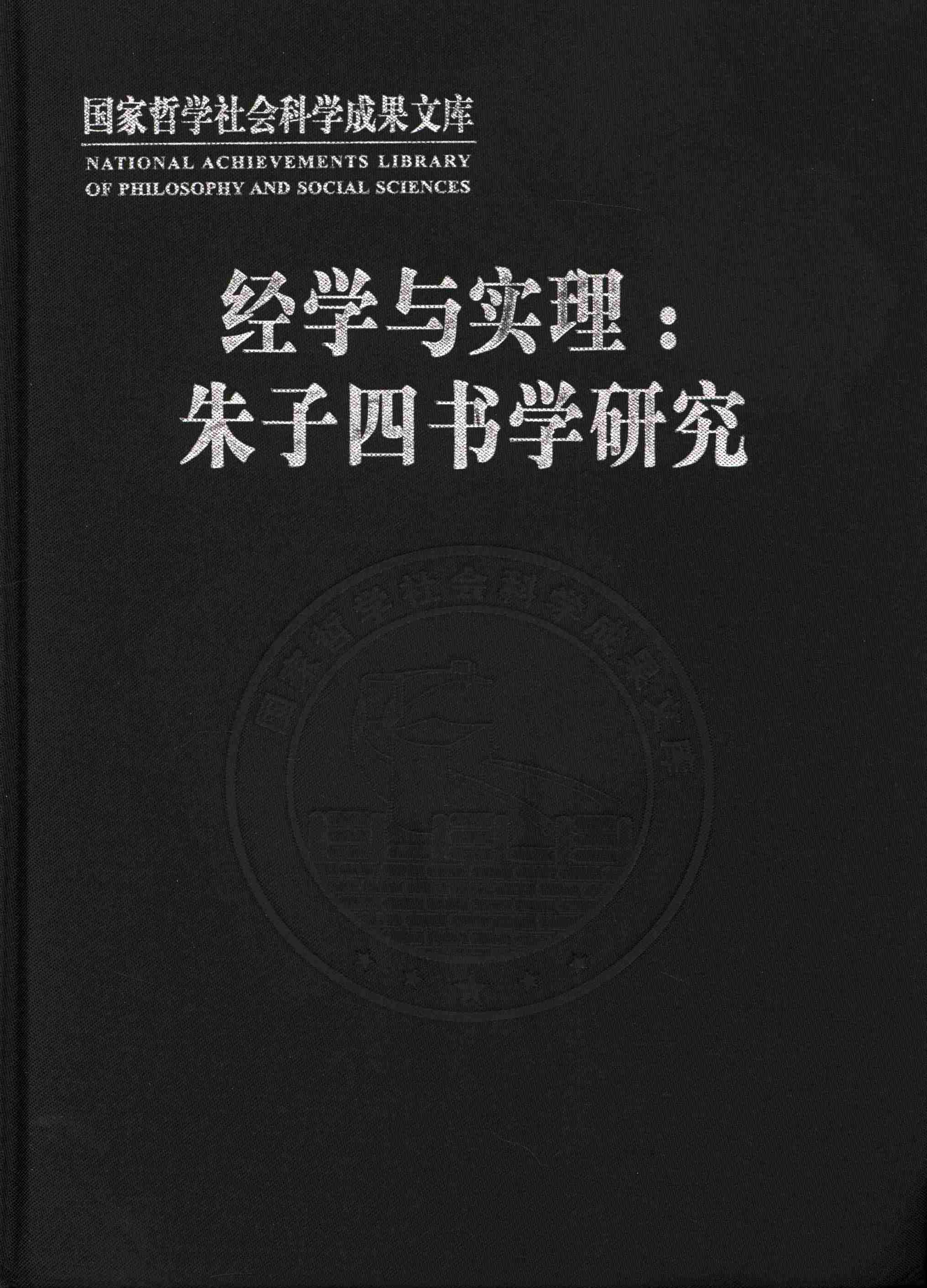二 儒佛之辨:辨张无垢《中庸解》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44 |
| 颗粒名称: | 二 儒佛之辨:辨张无垢《中庸解》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129-139 |
| 摘要: | 这段文字描述了朱熹在接触理学之前受到禅学和家学的影响,对《中庸》有了一定了解。在延平的引导下,他开始接受并理解“理一分殊”的学说,这一学说的接受对他的中庸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延平逝世后,朱熹继续对《中庸》展开探索,并撰写了《杂学辨》一书,批驳了其他学派的解读,尤其是对张无垢的《中庸解》进行了重点批评。他认为张九成的佛学印迹特深,危害最大,开启了此后朱子最大对手陆象山之学。朱子选择批评张九成等名人,体现了他的策略和勇气。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延平逝世后,朱子继续对《中庸》展开艰难探索,一个阶段总结性成果是在丙戌(1166年)冬撰写的《杂学辨》,该书分别批驳了《苏氏易学解》、《苏黄门老子解》、《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其中尤以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其实质是思想战线的一次交锋,通过划清儒与释老的界线,端正士子为学方向。故朱子特意挑选了在士子之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贵显名誉之士”,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士子会因崇拜名人而迷恋名人所崇拜的异端之学。“未论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选择张九成等名人加以批评体现了朱子的策略和勇气。朱子始终认为张九成佛学印迹特深,危害最大,“张公以佛语释儒书,其迹尤著。”九成与朱子所处时代最相近,对当时士子的影响最直接广泛;在学术渊源上与朱子又具有“血缘关系”,同出于龟山门下,与谢良佐亦有关联;且开启了此后朱子最大对手陆象山之学。对于这样一位“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释”的代表人物,朱子当然视为清理门户的首选了。朱子对无垢的著作有个基本判定,即“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效用之危害则是,“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故朱子毫不犹豫地亮出清理门户的卫道身份,以拯救世道人心,“尝欲为之论辨,以晓当世之惑”。朱子对张九成以禅解儒说的广为甚行极其担心,将其学说之流行喻为洪水猛兽。①无垢著作甚多,其佞佛最深者,则为《中庸解》,故朱子挑出全书五十二条予以批驳,“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②主要围绕性论、戒惧、忠恕、诚论、知行诸核心问题展开论辨,体现了朱子的佛学水平,反映出朱子此时中庸学的不成熟之处,显示出其对章句之学与辟佛老的一贯坚持,可谓早年学术之总结。
(一)性论:赞性、率性、觉性、见性
朱子对张氏性论的批评,针对其赞性、率性、觉性、见性说展开,体现了朱子此时对性的认识。“赞性”“体之为己物”。张氏认为天命之性说并没有对性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不过是称赞“性”之可贵,因其来源于天,是一普遍公共之状态,并未为人所个别拥有而“收为己物”。在率性之道时方才体性为自身之物,进入于五常之内。修道之教则表现为仁行于父子之类。“天命之谓性,第赞性之可贵耳,未见人收之为己物也。率性之谓道,则人体之为己物,而入于仁义礼智中矣……修道之谓教,则仁行于父子。”①朱子认为天命之性正是道出性之所以为性的本质所在,表明性是天赋人受,是义理之本原,非称赞性之可贵。并引董仲舒命为天令,性为生质说为证。反驳性“未为己物”说,既谓之“性”,则已经为人所禀赋了,否则无性可言。再则,性亦不存在待人“收为己物”。故张氏此说犯有两误。一方面人之生即同时禀赋天命之性,性与人俱生,否则人不成其为人矣。另一方面,性并非实存有形有方位之物,可收放储存,故以物言性不妥。“体之为己物”说亦不妥。性的内容乃是天赋之仁义礼智,并不需要待人去体验之,然后才入于五常之中。此皆不知为学大本妄加穿凿之病。再则仁行于父子等乃是率性之道而非修道之教,张氏颠倒道、教次序而不知。朱子晚年《章句》则从“理”立论,提出“性即理”说,强调性的普遍公共性,与此仅从人性上理解性不同。
“率性学者事,修教圣人功”。针对道、教关系,张氏作出两层区分:一是指圣人与学者的不同层次:率性是学者之事,以戒惧为工夫,修教则是圣人功用。修教之所以是圣人功用,是学者经由戒惧工夫而深入性之本原,达到天命在我境界后才能够发生的,以推行五常之教为主的效用。“方率性时,戒慎恐惧,此学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谓天命在我,然后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教,以幸于天下。”②朱子认为,率性之谓道是阐释道之为道的根据,意为遵循性之本然即是道,并非学者之事,亦不涉及戒惧之说。而修道为教是通贯上下的,贯穿了制定施为者圣人和修习者贤人。批评张氏直到深入性本原之说方才推行教的说法不合事理,将会导致遗弃伦理教化的后果,偏离儒家主旨,陷于释氏之说。“则是圣人未至此地之时,未有人伦之教……凡此皆烂漫无根之言,乃释氏之绪余,非吾儒之本指也。”二是指“离位”与否。朱子认为,率性并未离开性之本位,修道之教不可以“离位”来论,性不可以本位言,否则如物体一般有方位处所,“言性有本位,则性有方所矣”,与圣贤对性的超越说法相违背。再则无垢上章以“率性”为求中工夫,就“求”而言,则有离位之义。若非离位,何来求?
无垢认为,颜子由戒惧工夫,于喜怒哀乐之中悟未发已发之几,一旦获得天命之性善者,即深入其中,而忘掉人欲,丧失我心,达到一种无我无人,无欲无识的境界。“颜子戒慎恐惧,超然悟未发已发之几于喜怒哀乐处,一得天命之性所谓善者,则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丧。”还进一步提出,颜子拳拳服膺,实际已达到与天理为一,毫无私欲,人我皆忘的境地。所谓圣人,不过知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处,故当于此处求之。朱子指出《中庸》此处并无悟意,喜怒哀乐本即是性,中节即善,不存在得性与深入其善之说。否则,在此未悟之前,未得性而在性外乎?所谓“我心皆丧”说大大有害于理。张氏的“得性”说实际并非得到义,乃是领悟义。朱子为批评无垢,居然将“喜怒哀乐”之情直接等同于性,是非常罕见的(仅此一次)。尽管性由情显,但朱子成熟说法是喜怒哀乐是情,未发才是性,情有中节不中节之分,故不能直接说喜怒哀乐是性。
针对“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张氏提出人就是性,以人治人就是以我性觉彼性。“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觉彼之性。”①朱子指出,此非经文本意,乃释氏说。张氏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天命谓性,性无彼此之分,为天下公共之理,其理一也。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为人天生所固有,不存在得失假借之可能,故无法“以”之。张氏将见性与由乎中庸结合论述。“使其由此见性,则自然由乎中庸,而向来无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扫不见迹矣。”认为如有人能因他人之觉悟而见其本性,则自然能够实现中庸。而此前言行之无物无常,皆扫除无遗了无痕迹矣。朱子予以批驳:“愚谓‘见性’本释氏语,盖一见则已矣,儒者则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养而充之,以至于尽,其用力有渐,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际一有懈焉,则几微之间,所害多矣。”②指出见性本佛学术语,指证悟到佛性本空。儒者则言知性,由知性而进于存养扩充,以至于尽性。此本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儒佛之别在于:佛以见性为终极目的,见性之后更无余事。儒者则要历经由知性到尽性的长期充养扩充过程,需要在日用之间作持久的实践积累之功。佛学者虽有自命不凡,宣称见到性空者,但其人格修养、习气欲望则和常人一般,并未见其实有所得之处。张氏之说正是如此。张氏认为若诚呈现出来,则己性,以及人性、物性直至天地之性皆能呈现。朱子指出,《中庸》本言至诚尽性,而非诚见性见,“见”与“尽”意义大不相同。此不同正是儒佛所别:佛氏以见性为极致,而不知儒者尽性之广大。“见字与尽字意义逈别,大率释氏以见性成佛为极,而不知圣人尽性之大。”①
(二)戒慎恐惧:“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
张氏对戒慎恐惧极为重视,视为全篇枢纽,反复言说。仅就朱子所引52条来看,论及戒惧者即有17条之多,朱子对此痛加批评。张氏认为戒惧是未发以前工夫,使内心达到毫无私欲的状态。“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朱子则认为戒慎恐惧是已发,未发之前是天理浑然,“愚谓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②这和他以后的看法恰好颠倒,在中和之悟后他将戒慎恐惧当作未发,慎独当作已发。张氏进一步提出,通过戒慎恐惧工夫来存养喜怒哀乐之情感,以获得中和境界,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而朱子则从“本然、自然”的立场予以反驳,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乃是本然具有之中,发而中节,是其本然之和,中和是一本然状态而非人力所能为。天地位、万物育亦是理的自然发用。朱子此时承袭延平说,认为中和乃“一篇之指要”,晚年改变之,采用龟山全章乃一篇体要说。
以戒惧之说来贯穿《中庸》,实为张氏《中庸解》一大特色。在张氏看来,戒慎恐惧可解释《中庸》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如张氏认为“无忧者其惟文王”中“无忧”的原因在于:通过戒惧工夫达到无所不中和的境界;认为“博学者,戒慎恐惧,非一事也。”认为“大莫能载小莫能破”的原因在于“以其戒慎恐惧,察于微茫之功”也。朱子皆驳斥之,指出因张氏以戒惧一说横贯《中庸》全书,故屡屡造成牵合附会之病。“张氏戒慎恐惧二句,横贯《中庸》一篇之中,其牵合附会,连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①张氏如此重视戒惧,用以解释全篇,是因为他认为中庸之道正是从戒惧工夫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君子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朱子批评“酝酿”不对,盖中庸之道乃天理自然,终始存在,并非因酝酿而产生。此批评亦未见得贴切,张氏酝酿与戒慎恐惧并列,指工夫之长久义,并非形容中庸之自然。
(三)辨忠恕:“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张氏对忠恕的阐发,遭到朱子最严厉批评,成为朱子最不能容忍的解释,认为其言“最害理”。他说: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责己也,知己之难克,然后知天下之未见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②
在忠、恕的界定上,张氏继承程门之说而又有重大偏离,其肯定恕来源于忠符合程门之义,但认为忠是责己、克己,恕是饶人、恕人之说则不合程门说。程子明确肯定“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故朱子肯定无垢“恕由忠生”说可取,但对“恕”的理解有很大问题。
愚谓恕由忠生,明道、谢子、侯子盖尝言之。然其为说,与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则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为义,本不如此。③
朱子解尽己为竭尽全部心力而毫无私意,推己则是在尽己基础上推扩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絜矩之道。张氏提出,一己之私难以克除,唯有见性者方能做到完全克除己私,明乎此,故对凡未能克除己私者、未能见性者皆加以宽恕,此即忠恕义。显然,张氏把忠理解为严以责己、恕为宽以待人。朱子批评张氏是以一己之私来对待天下之人。忠恕的本质是表现为如何对待人己关系,他引张载说指出应以责求他人之心来要求自己,以爱护自己之心来爱护别人。只有抱有责人以责己、爱己以爱人、众人以望人,才能做到人我之间心意相通、彼此一致,而各得其所、各守其则。朱子指出,如张氏之说,因己私难克而容忍他人私心之存在,以至于由此而发展为罪恶之事,其后果是诱导天下人皆流于禽兽境地,完全背离了儒家忠恕之教。朱子对张氏的忠恕批评一生保持未变,①并将张载的忠恕解写入《章句》。
朱子进而剖析张氏产生严重误解的原因在于章句文义理解的偏差。张氏主张此处断为四句,分别在“父”、“君”、“兄”、“之”后断。如张氏解,则理解为子父、臣君、兄弟、朋友之间的单边关系,即深入考察儿子侍奉父亲所应尽之道,而反思自身亦未能做到。因此,未敢要求父亲对儿子给予爱护之道。朱子指出张氏断句有误,“察”字理解有误。
愚谓此四句当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绝处,求犹责也,所责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则自有所未能。……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则安敢责父之爱子乎?”则是君臣父子漠然为路人矣。……盖其驰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详,故因以误为此说。②
此处当分为八句,应在子、臣、弟、友之后点断,这种断句的差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理解,朱子理解为子父、父子双边关系,即要求儿子对自己应做的,自己对父亲也没有做到,此时的“我”处于上下交错的人际关系中,“求”与“责”是同义(而非张氏的“察”)。当由张子《正蒙》“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说来自我劝勉,推扩,而并非如上章张氏所云“因为自身私意难以克除而容忍他人之私”,这样对私意的包容必然导致人心的堕落。张氏之误源于其深受佛学用心于空虚高明之所的影响,对文本章句未加详细审查。
“当于忠恕卜之”。张氏还提出,应当从是否做到忠恕来审察戒慎恐惧的效果,即戒惧为工夫,忠恕为效用;忠恕之效用又当自父母身上审察之。盖忠恕最切近者为事父母。“张云:欲知戒慎恐惧之效,当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当于父母卜之。”①朱子批评张氏之说牵强无理,视至尊的父母为卜算之物,其说已陷入“二本”而不知。张氏显然是比喻手法,朱子过于从字面理解。
(四)诚:无息为诚、知诚行诚、注诚于身
“认专为诚”与“无息为诚”。张氏指出学者多将“诚”误认为“专”,至诚本不息,若专则息矣。语言断绝,应对酬酢皆离开本位也。“世之论诚者多错认专为诚,夫至诚无息,专非诚也。以专为诚则是语言寝处,应对酬酢,皆离本位矣。”朱子予以反驳:“专”固然不足以表达“诚”之内涵,但如张氏以“无息”为诚,亦是错误。至诚之效用是不息,而非因无息方有诚之名义也。“离本位”亦非圣人说,乃是佛老之见。此意朱子始终未变,故《章句》言“诚故不息”。
此外,朱子还批评张氏“行诚不若知诚明,知诚不若行诚大”说,提出儒家思想中只有存诚、思诚,而无行诚说。通过思诚、存诚工夫,使诚内在于己,则其所行所发皆出于诚、合乎诚。而行诚说则把诚视为一个外在于己的事物看待,造成自我与诚的分裂,完全背离了诚之意义,后果极其严重。至于诵《孝经》御贼之说,其误在于事理不明而有迂腐愚蠢之弊,与诚无关。诵《仁王经》者,乃异端之见。
张氏关于诚的效用确有许多近乎佛老的过高之说。如他指出,注诚于身则诚,于亲则悦,于友则信,于君民则治。朱子指出,若能明善则自然诚身,此是理之自然。由身诚至于亲、友、君、民皆然,此是德盛自然所至。若言“注之而然”,则认为诚身与亲、友、君、民存在距离,尚须注入之过程,已陷入最大之不诚。再如“不诚无物”解为“吾诚一往,则耳目口鼻皆坏矣”说确实怪异。②朱子提出,诚不可以“吾”言,盖诚为本体,故不必言往。耳目口鼻,亦无一旦遽坏之理。
张氏认为,诚明谓之性,是指资质上等之人修道自得而合乎圣人教化;明诚谓之教,则是由遵从圣人教化以达到上智境界者。若有上智自得而不合乎圣人教化者,则为异端。朱子认为张氏对诚明理解的偏颇,适反映出其傲然自处于诚明之境,而实际陷于异端之学。此说的目的,是想通过“改头换面、阴予阳跻”的方式来达到掩盖其佛老之迹,避免别人怀疑的目的,此恰是其最大不诚之处。其实,张氏此说意在强调“合圣人之教”的重要性,以划清与佛老的界限,朱子的理解似乎有点“草木皆兵”之意味。
“变化天地皆在于我”。至诚无息章张氏提出天地之自章、自编、自成,其动力皆在于至诚不息之圣人,天地亦因此至诚不息而产生造化之妙用。朱子从文义与事理两面作出批驳:
张氏首要之误在于对本章文义理解有差,所谓不见、不动、无为皆是言至诚之理的效用,此理与天地之道相合。张氏则以为此言圣人至诚之效用,使天地彰明变化,不仅文义不通,且不合事理。而“天地自此造化”说更加危险奇怪,颠倒了圣人与天地上下关系,若如此说,则圣人反而造化天地,推测张氏说之蔽源于佛学“心法起灭天地”之说。①
(五)知论:“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
“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张氏指出,如果做到了智仁勇,则对九经无所期待用力而九经自然得到实行,一一合乎其道。“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朱子指出此说会造成不良后果。若如张氏解,则九经皆为多余之说,张氏一心仰慕佛学高远虚灵之说而忽视了实地事为之功。
张氏指出,常人只是知道用知识去品评判断是非,而不知用之于戒惧恐惧工夫。若能“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方为大知。此说显然意在突出道德实践之知的优先性。朱子由此读出佛学的印迹,“故诠品是非,乃穷理之事,亦学者之急务也。岂释氏所称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遗意耶?呜呼,斯言也,其儒释所以分之始与!”朱子以穷理说批评张氏的移是非之心说,认为对事理是非的判断是天下正理,是一切知之开端,是人之本质和必须之当务,是行事合乎天理的必要前提。张氏完全忽视这一面,任其私知而不循天理,走向佛氏不问是非,仅求心证之途。讲求是非之知正可以作为判定儒释之分的第一标尺。有趣的是,朱子所引“直取无上菩提”与上文延平告诫朱子的“一超直入”说正好相应,可见朱子今非昔比。
张氏提出对格物的看法:“格物致知之学,内而一念,外而万事,无不穷其终始,穷而又穷,以至于极尽之地,人欲都尽,一旦廓然,则性善昭昭无可疑矣。”格物致知乃是从内外两面用功,包括内在意念与外在事物,皆要探究其终始,反复用功,达到人欲皆无的极致之地,此时心底廓然,唯有人性之善昭昭显露。由格物证悟到性善,使性善呈露彰显。朱子指出,格物当以二程之说为准,张氏之说乃是佛氏“看话头”的做法,背离了圣贤本旨,其病与吕本中《大学解》一致。
(六)章句工夫:“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
朱子在从学延平时即体现出好章句学的特点,给延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章句文义的辨析,亦淋漓尽致体现于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批评中。如前述对“所求乎子”一段的章句理解,朱子一生未能释怀,晚年还以此为典型批评以章句之学为陋的看法,提出“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的强势表述,突出了章句在义理理解中的优先性。这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章句之学于朱子而言,不是一般的文字解释,而是为学为道的工夫,是必要工夫,是首要、根本工夫。他说:
张子韶说《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点做一句。……而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贺孙。①
就短短五十二条《中庸解》来看,朱子多次指出张氏对文本的断句、字义理解有误,导致义理产生重大偏差。其中尤以“察”字的解释为有意味。除上引“所求乎子以事父”以“求”为“察”外,在“言顾行”的理解中,亦指出张氏将“顾”理解为“察”过于牵合,张氏所犯毛病在于就某一字义任意推衍,而不顾其是否合适可取。典型者如“戒慎恐惧”,忠恕、知仁勇、发育峻极等,张氏亦是将其贯穿全篇,任意使用。对费而隐章主旨的把握,“察”字亦很关键,朱子批评张氏把“上下察”的“察”解为“审察”不妥(朱子早年亦如此解),乃是“著察”义,如此才符合子思之义。张氏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已通过戒惧工夫开始致察,“察”无所不在。通过此“察”来养中和,在未发已发之间起为中和,使中和彰显之。朱子批评“起而为中和”说大悖理而不可理喻。
总之,朱子认为章句之学的疏略是导致张氏该书(学术)产生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特点的重要原因。朱子对张氏的评价是,“张氏之书,变怪惊眩盖不少矣。犹以为无有,不知更欲如何,乃为变怪惊眩哉。”①如张氏把“此天地之所以为大”释为由此可见夫子实未尝死,天地乃夫子之乾坤。朱子认为“不死之云,变怪骇人而实无余味。”②
(一)性论:赞性、率性、觉性、见性
朱子对张氏性论的批评,针对其赞性、率性、觉性、见性说展开,体现了朱子此时对性的认识。“赞性”“体之为己物”。张氏认为天命之性说并没有对性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不过是称赞“性”之可贵,因其来源于天,是一普遍公共之状态,并未为人所个别拥有而“收为己物”。在率性之道时方才体性为自身之物,进入于五常之内。修道之教则表现为仁行于父子之类。“天命之谓性,第赞性之可贵耳,未见人收之为己物也。率性之谓道,则人体之为己物,而入于仁义礼智中矣……修道之谓教,则仁行于父子。”①朱子认为天命之性正是道出性之所以为性的本质所在,表明性是天赋人受,是义理之本原,非称赞性之可贵。并引董仲舒命为天令,性为生质说为证。反驳性“未为己物”说,既谓之“性”,则已经为人所禀赋了,否则无性可言。再则,性亦不存在待人“收为己物”。故张氏此说犯有两误。一方面人之生即同时禀赋天命之性,性与人俱生,否则人不成其为人矣。另一方面,性并非实存有形有方位之物,可收放储存,故以物言性不妥。“体之为己物”说亦不妥。性的内容乃是天赋之仁义礼智,并不需要待人去体验之,然后才入于五常之中。此皆不知为学大本妄加穿凿之病。再则仁行于父子等乃是率性之道而非修道之教,张氏颠倒道、教次序而不知。朱子晚年《章句》则从“理”立论,提出“性即理”说,强调性的普遍公共性,与此仅从人性上理解性不同。
“率性学者事,修教圣人功”。针对道、教关系,张氏作出两层区分:一是指圣人与学者的不同层次:率性是学者之事,以戒惧为工夫,修教则是圣人功用。修教之所以是圣人功用,是学者经由戒惧工夫而深入性之本原,达到天命在我境界后才能够发生的,以推行五常之教为主的效用。“方率性时,戒慎恐惧,此学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谓天命在我,然后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教,以幸于天下。”②朱子认为,率性之谓道是阐释道之为道的根据,意为遵循性之本然即是道,并非学者之事,亦不涉及戒惧之说。而修道为教是通贯上下的,贯穿了制定施为者圣人和修习者贤人。批评张氏直到深入性本原之说方才推行教的说法不合事理,将会导致遗弃伦理教化的后果,偏离儒家主旨,陷于释氏之说。“则是圣人未至此地之时,未有人伦之教……凡此皆烂漫无根之言,乃释氏之绪余,非吾儒之本指也。”二是指“离位”与否。朱子认为,率性并未离开性之本位,修道之教不可以“离位”来论,性不可以本位言,否则如物体一般有方位处所,“言性有本位,则性有方所矣”,与圣贤对性的超越说法相违背。再则无垢上章以“率性”为求中工夫,就“求”而言,则有离位之义。若非离位,何来求?
无垢认为,颜子由戒惧工夫,于喜怒哀乐之中悟未发已发之几,一旦获得天命之性善者,即深入其中,而忘掉人欲,丧失我心,达到一种无我无人,无欲无识的境界。“颜子戒慎恐惧,超然悟未发已发之几于喜怒哀乐处,一得天命之性所谓善者,则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丧。”还进一步提出,颜子拳拳服膺,实际已达到与天理为一,毫无私欲,人我皆忘的境地。所谓圣人,不过知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处,故当于此处求之。朱子指出《中庸》此处并无悟意,喜怒哀乐本即是性,中节即善,不存在得性与深入其善之说。否则,在此未悟之前,未得性而在性外乎?所谓“我心皆丧”说大大有害于理。张氏的“得性”说实际并非得到义,乃是领悟义。朱子为批评无垢,居然将“喜怒哀乐”之情直接等同于性,是非常罕见的(仅此一次)。尽管性由情显,但朱子成熟说法是喜怒哀乐是情,未发才是性,情有中节不中节之分,故不能直接说喜怒哀乐是性。
针对“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张氏提出人就是性,以人治人就是以我性觉彼性。“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觉彼之性。”①朱子指出,此非经文本意,乃释氏说。张氏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天命谓性,性无彼此之分,为天下公共之理,其理一也。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为人天生所固有,不存在得失假借之可能,故无法“以”之。张氏将见性与由乎中庸结合论述。“使其由此见性,则自然由乎中庸,而向来无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扫不见迹矣。”认为如有人能因他人之觉悟而见其本性,则自然能够实现中庸。而此前言行之无物无常,皆扫除无遗了无痕迹矣。朱子予以批驳:“愚谓‘见性’本释氏语,盖一见则已矣,儒者则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养而充之,以至于尽,其用力有渐,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际一有懈焉,则几微之间,所害多矣。”②指出见性本佛学术语,指证悟到佛性本空。儒者则言知性,由知性而进于存养扩充,以至于尽性。此本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儒佛之别在于:佛以见性为终极目的,见性之后更无余事。儒者则要历经由知性到尽性的长期充养扩充过程,需要在日用之间作持久的实践积累之功。佛学者虽有自命不凡,宣称见到性空者,但其人格修养、习气欲望则和常人一般,并未见其实有所得之处。张氏之说正是如此。张氏认为若诚呈现出来,则己性,以及人性、物性直至天地之性皆能呈现。朱子指出,《中庸》本言至诚尽性,而非诚见性见,“见”与“尽”意义大不相同。此不同正是儒佛所别:佛氏以见性为极致,而不知儒者尽性之广大。“见字与尽字意义逈别,大率释氏以见性成佛为极,而不知圣人尽性之大。”①
(二)戒慎恐惧:“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
张氏对戒慎恐惧极为重视,视为全篇枢纽,反复言说。仅就朱子所引52条来看,论及戒惧者即有17条之多,朱子对此痛加批评。张氏认为戒惧是未发以前工夫,使内心达到毫无私欲的状态。“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朱子则认为戒慎恐惧是已发,未发之前是天理浑然,“愚谓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②这和他以后的看法恰好颠倒,在中和之悟后他将戒慎恐惧当作未发,慎独当作已发。张氏进一步提出,通过戒慎恐惧工夫来存养喜怒哀乐之情感,以获得中和境界,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而朱子则从“本然、自然”的立场予以反驳,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乃是本然具有之中,发而中节,是其本然之和,中和是一本然状态而非人力所能为。天地位、万物育亦是理的自然发用。朱子此时承袭延平说,认为中和乃“一篇之指要”,晚年改变之,采用龟山全章乃一篇体要说。
以戒惧之说来贯穿《中庸》,实为张氏《中庸解》一大特色。在张氏看来,戒慎恐惧可解释《中庸》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如张氏认为“无忧者其惟文王”中“无忧”的原因在于:通过戒惧工夫达到无所不中和的境界;认为“博学者,戒慎恐惧,非一事也。”认为“大莫能载小莫能破”的原因在于“以其戒慎恐惧,察于微茫之功”也。朱子皆驳斥之,指出因张氏以戒惧一说横贯《中庸》全书,故屡屡造成牵合附会之病。“张氏戒慎恐惧二句,横贯《中庸》一篇之中,其牵合附会,连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①张氏如此重视戒惧,用以解释全篇,是因为他认为中庸之道正是从戒惧工夫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君子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朱子批评“酝酿”不对,盖中庸之道乃天理自然,终始存在,并非因酝酿而产生。此批评亦未见得贴切,张氏酝酿与戒慎恐惧并列,指工夫之长久义,并非形容中庸之自然。
(三)辨忠恕:“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张氏对忠恕的阐发,遭到朱子最严厉批评,成为朱子最不能容忍的解释,认为其言“最害理”。他说: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责己也,知己之难克,然后知天下之未见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②
在忠、恕的界定上,张氏继承程门之说而又有重大偏离,其肯定恕来源于忠符合程门之义,但认为忠是责己、克己,恕是饶人、恕人之说则不合程门说。程子明确肯定“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故朱子肯定无垢“恕由忠生”说可取,但对“恕”的理解有很大问题。
愚谓恕由忠生,明道、谢子、侯子盖尝言之。然其为说,与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则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为义,本不如此。③
朱子解尽己为竭尽全部心力而毫无私意,推己则是在尽己基础上推扩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絜矩之道。张氏提出,一己之私难以克除,唯有见性者方能做到完全克除己私,明乎此,故对凡未能克除己私者、未能见性者皆加以宽恕,此即忠恕义。显然,张氏把忠理解为严以责己、恕为宽以待人。朱子批评张氏是以一己之私来对待天下之人。忠恕的本质是表现为如何对待人己关系,他引张载说指出应以责求他人之心来要求自己,以爱护自己之心来爱护别人。只有抱有责人以责己、爱己以爱人、众人以望人,才能做到人我之间心意相通、彼此一致,而各得其所、各守其则。朱子指出,如张氏之说,因己私难克而容忍他人私心之存在,以至于由此而发展为罪恶之事,其后果是诱导天下人皆流于禽兽境地,完全背离了儒家忠恕之教。朱子对张氏的忠恕批评一生保持未变,①并将张载的忠恕解写入《章句》。
朱子进而剖析张氏产生严重误解的原因在于章句文义理解的偏差。张氏主张此处断为四句,分别在“父”、“君”、“兄”、“之”后断。如张氏解,则理解为子父、臣君、兄弟、朋友之间的单边关系,即深入考察儿子侍奉父亲所应尽之道,而反思自身亦未能做到。因此,未敢要求父亲对儿子给予爱护之道。朱子指出张氏断句有误,“察”字理解有误。
愚谓此四句当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绝处,求犹责也,所责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则自有所未能。……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则安敢责父之爱子乎?”则是君臣父子漠然为路人矣。……盖其驰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详,故因以误为此说。②
此处当分为八句,应在子、臣、弟、友之后点断,这种断句的差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理解,朱子理解为子父、父子双边关系,即要求儿子对自己应做的,自己对父亲也没有做到,此时的“我”处于上下交错的人际关系中,“求”与“责”是同义(而非张氏的“察”)。当由张子《正蒙》“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说来自我劝勉,推扩,而并非如上章张氏所云“因为自身私意难以克除而容忍他人之私”,这样对私意的包容必然导致人心的堕落。张氏之误源于其深受佛学用心于空虚高明之所的影响,对文本章句未加详细审查。
“当于忠恕卜之”。张氏还提出,应当从是否做到忠恕来审察戒慎恐惧的效果,即戒惧为工夫,忠恕为效用;忠恕之效用又当自父母身上审察之。盖忠恕最切近者为事父母。“张云:欲知戒慎恐惧之效,当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当于父母卜之。”①朱子批评张氏之说牵强无理,视至尊的父母为卜算之物,其说已陷入“二本”而不知。张氏显然是比喻手法,朱子过于从字面理解。
(四)诚:无息为诚、知诚行诚、注诚于身
“认专为诚”与“无息为诚”。张氏指出学者多将“诚”误认为“专”,至诚本不息,若专则息矣。语言断绝,应对酬酢皆离开本位也。“世之论诚者多错认专为诚,夫至诚无息,专非诚也。以专为诚则是语言寝处,应对酬酢,皆离本位矣。”朱子予以反驳:“专”固然不足以表达“诚”之内涵,但如张氏以“无息”为诚,亦是错误。至诚之效用是不息,而非因无息方有诚之名义也。“离本位”亦非圣人说,乃是佛老之见。此意朱子始终未变,故《章句》言“诚故不息”。
此外,朱子还批评张氏“行诚不若知诚明,知诚不若行诚大”说,提出儒家思想中只有存诚、思诚,而无行诚说。通过思诚、存诚工夫,使诚内在于己,则其所行所发皆出于诚、合乎诚。而行诚说则把诚视为一个外在于己的事物看待,造成自我与诚的分裂,完全背离了诚之意义,后果极其严重。至于诵《孝经》御贼之说,其误在于事理不明而有迂腐愚蠢之弊,与诚无关。诵《仁王经》者,乃异端之见。
张氏关于诚的效用确有许多近乎佛老的过高之说。如他指出,注诚于身则诚,于亲则悦,于友则信,于君民则治。朱子指出,若能明善则自然诚身,此是理之自然。由身诚至于亲、友、君、民皆然,此是德盛自然所至。若言“注之而然”,则认为诚身与亲、友、君、民存在距离,尚须注入之过程,已陷入最大之不诚。再如“不诚无物”解为“吾诚一往,则耳目口鼻皆坏矣”说确实怪异。②朱子提出,诚不可以“吾”言,盖诚为本体,故不必言往。耳目口鼻,亦无一旦遽坏之理。
张氏认为,诚明谓之性,是指资质上等之人修道自得而合乎圣人教化;明诚谓之教,则是由遵从圣人教化以达到上智境界者。若有上智自得而不合乎圣人教化者,则为异端。朱子认为张氏对诚明理解的偏颇,适反映出其傲然自处于诚明之境,而实际陷于异端之学。此说的目的,是想通过“改头换面、阴予阳跻”的方式来达到掩盖其佛老之迹,避免别人怀疑的目的,此恰是其最大不诚之处。其实,张氏此说意在强调“合圣人之教”的重要性,以划清与佛老的界限,朱子的理解似乎有点“草木皆兵”之意味。
“变化天地皆在于我”。至诚无息章张氏提出天地之自章、自编、自成,其动力皆在于至诚不息之圣人,天地亦因此至诚不息而产生造化之妙用。朱子从文义与事理两面作出批驳:
张氏首要之误在于对本章文义理解有差,所谓不见、不动、无为皆是言至诚之理的效用,此理与天地之道相合。张氏则以为此言圣人至诚之效用,使天地彰明变化,不仅文义不通,且不合事理。而“天地自此造化”说更加危险奇怪,颠倒了圣人与天地上下关系,若如此说,则圣人反而造化天地,推测张氏说之蔽源于佛学“心法起灭天地”之说。①
(五)知论:“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
“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张氏指出,如果做到了智仁勇,则对九经无所期待用力而九经自然得到实行,一一合乎其道。“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朱子指出此说会造成不良后果。若如张氏解,则九经皆为多余之说,张氏一心仰慕佛学高远虚灵之说而忽视了实地事为之功。
张氏指出,常人只是知道用知识去品评判断是非,而不知用之于戒惧恐惧工夫。若能“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方为大知。此说显然意在突出道德实践之知的优先性。朱子由此读出佛学的印迹,“故诠品是非,乃穷理之事,亦学者之急务也。岂释氏所称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遗意耶?呜呼,斯言也,其儒释所以分之始与!”朱子以穷理说批评张氏的移是非之心说,认为对事理是非的判断是天下正理,是一切知之开端,是人之本质和必须之当务,是行事合乎天理的必要前提。张氏完全忽视这一面,任其私知而不循天理,走向佛氏不问是非,仅求心证之途。讲求是非之知正可以作为判定儒释之分的第一标尺。有趣的是,朱子所引“直取无上菩提”与上文延平告诫朱子的“一超直入”说正好相应,可见朱子今非昔比。
张氏提出对格物的看法:“格物致知之学,内而一念,外而万事,无不穷其终始,穷而又穷,以至于极尽之地,人欲都尽,一旦廓然,则性善昭昭无可疑矣。”格物致知乃是从内外两面用功,包括内在意念与外在事物,皆要探究其终始,反复用功,达到人欲皆无的极致之地,此时心底廓然,唯有人性之善昭昭显露。由格物证悟到性善,使性善呈露彰显。朱子指出,格物当以二程之说为准,张氏之说乃是佛氏“看话头”的做法,背离了圣贤本旨,其病与吕本中《大学解》一致。
(六)章句工夫:“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
朱子在从学延平时即体现出好章句学的特点,给延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章句文义的辨析,亦淋漓尽致体现于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批评中。如前述对“所求乎子”一段的章句理解,朱子一生未能释怀,晚年还以此为典型批评以章句之学为陋的看法,提出“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的强势表述,突出了章句在义理理解中的优先性。这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章句之学于朱子而言,不是一般的文字解释,而是为学为道的工夫,是必要工夫,是首要、根本工夫。他说:
张子韶说《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点做一句。……而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贺孙。①
就短短五十二条《中庸解》来看,朱子多次指出张氏对文本的断句、字义理解有误,导致义理产生重大偏差。其中尤以“察”字的解释为有意味。除上引“所求乎子以事父”以“求”为“察”外,在“言顾行”的理解中,亦指出张氏将“顾”理解为“察”过于牵合,张氏所犯毛病在于就某一字义任意推衍,而不顾其是否合适可取。典型者如“戒慎恐惧”,忠恕、知仁勇、发育峻极等,张氏亦是将其贯穿全篇,任意使用。对费而隐章主旨的把握,“察”字亦很关键,朱子批评张氏把“上下察”的“察”解为“审察”不妥(朱子早年亦如此解),乃是“著察”义,如此才符合子思之义。张氏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已通过戒惧工夫开始致察,“察”无所不在。通过此“察”来养中和,在未发已发之间起为中和,使中和彰显之。朱子批评“起而为中和”说大悖理而不可理喻。
总之,朱子认为章句之学的疏略是导致张氏该书(学术)产生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特点的重要原因。朱子对张氏的评价是,“张氏之书,变怪惊眩盖不少矣。犹以为无有,不知更欲如何,乃为变怪惊眩哉。”①如张氏把“此天地之所以为大”释为由此可见夫子实未尝死,天地乃夫子之乾坤。朱子认为“不死之云,变怪骇人而实无余味。”②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