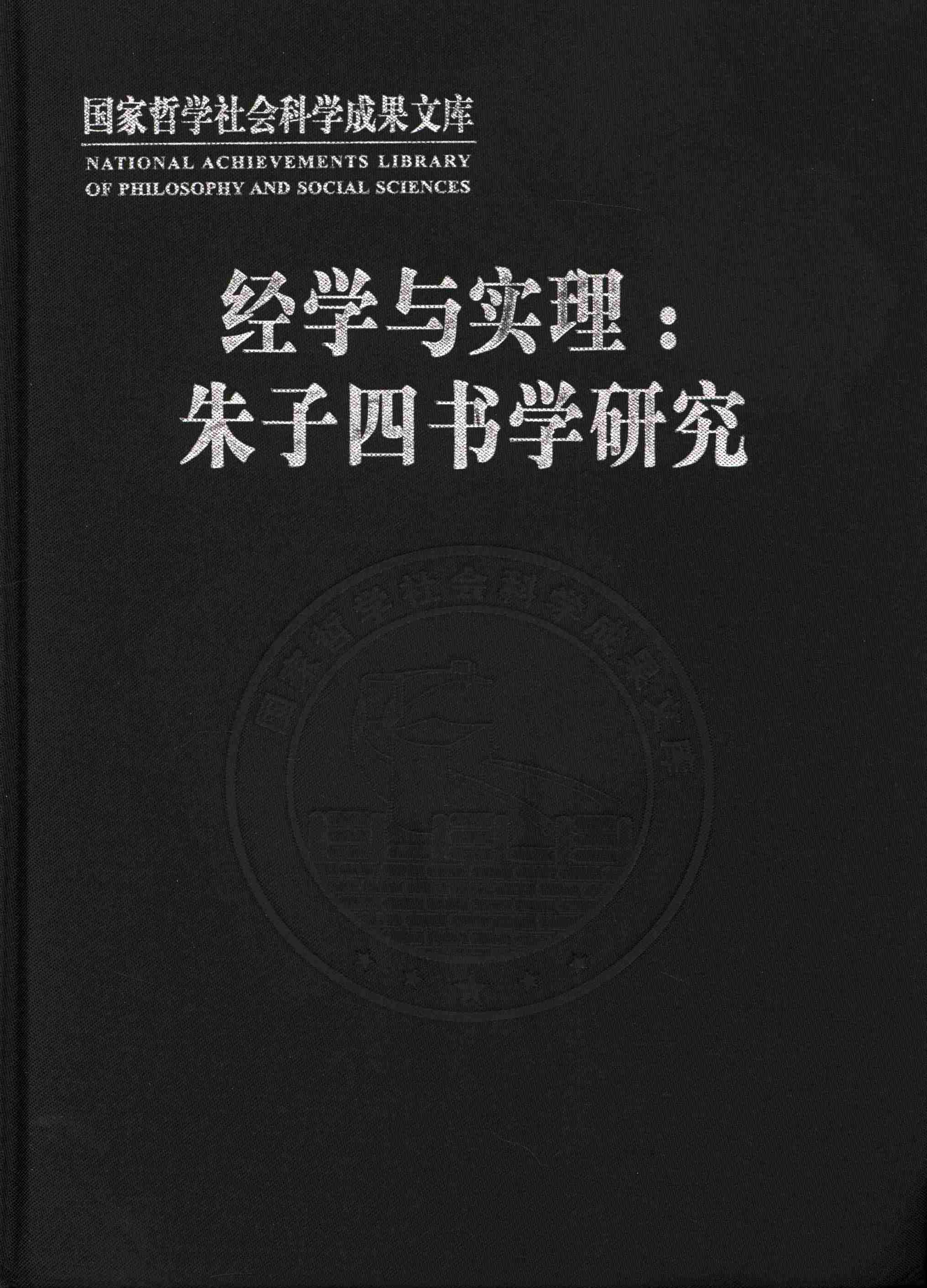一 忠一恕贯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25 |
| 颗粒名称: | 一 忠一恕贯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6 |
| 页码: | 89-94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对“忠恕”章的注释强调了忠恕的体用一贯义,认为忠是指尽己,恕是指推己。忠和恕都是从心上言,指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两种方式。朱子采用程颐的定义,并强调了尽己的极高要求。他还引用了大程子的说法,以仁、恕对言解忠、恕,强调了自然与勉强的区别。忠和恕的关系紧密,即本体即发用,不能替换为诚和仁。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朱子对“忠恕”章的注释以二程之说为基础,将自身看法揉入其中,阐发了忠恕体用一贯义。本章原文仅有35字,注文则多达500字,足为原文十数倍。原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③
“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朱子首先从圣人境界讲“一以贯之”,阐发“一以贯之”所体现的理事体用义。“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里仁》)圣人全体是理,作用出来即是理之显现。虽然呈现出的作用各不相同,然皆贯穿着同一之理,是同一下的差别,分殊中的普遍。当同一之理作用于具体事物时,就表现出一种自然差异,即理一分殊也。这个理是指天地万物共具的普遍同一之理,和它相对的则是具体特殊的事物。曾子通过持久不懈的日用工夫,达到了对具体事物分殊之理的理解,经过夫子点醒,最终了悟天地共具之理,才以“一以贯之”说表达之。①当然,朱子对理一分殊的认识主要还是从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角度着眼,以之解决以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故朱子在此将一贯之本体始终放在心上讲,突出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的关系,提出圣人心与理一,心尽万理,物我无间。
朱子新解在于将理本体与《中庸》诚本体相沟通,把圣人浑然一理与天地至诚无息说结合。天地有诚而万物得所,圣人显理而万事得当,道体具有真实自然,创生不已的特质,是天地殊异万物皆具之同理;万物各归其位,各尽其性,则是道体自然发用。据此凸显圣人一以贯之的真实存在,因为圣人在至诚意义上与天地相沟通,故能如天地本体对万物造化一般,历历可见,无处不在。“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论语集注·里仁》)朱子以一本万殊解释一以贯之,以诚为万物之本,万物为诚之用,和《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对应,皆是言理事体用的一多关系。“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论语集注·里仁》)弟子担心体用之说有分成两物之嫌,朱子认为体用一物,不可分离,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二者浑然一体。朱子还强调对于此理本体,不须多说,因为本体不可见,不可言,多说反而失其本意。“要之,‘至诚无息’一句,已自剩了。”②
忠体恕用。朱子采用程颐“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说来定义忠恕,忠即是尽己,恕即是推己。忠恕就是以己为中心对待己和他人的两种方式。忠和恕皆是从心上言,尽己和推己之己皆是指己之心。朱子对“尽己之心”的“尽”提出极高要求,认为当百分之百穷尽己心,不能有丝毫姑息和欠缺,否则就不是忠。“尽时须是十分尽得,方是尽。若七分尽得,三分未尽,也不是忠。”③至于如何尽己,就不仅是理论问题,而应当在日用事为上体验、印证,否则空说无益,反致偏离本义。朱子还从语言学角度,根据字形特点,采取《周礼疏》对忠恕的解释:“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此解更为突出了忠恕在心上的意味。朱子认为忠就是真实,“忠只是一个真实。”心中所具之理必须真实,否则无法发用出来,唯有真实,其发用才无不得当,轻重厚薄大小一一合宜,这同于《中庸》不诚无物说。批评“尽物之谓恕”说,因为恕之得名,只是推己,恕只是从尽己之忠流出,流而未尽也,“‘恕’字上着‘尽’字不得。”①
朱子引用大程子说,以仁、恕对言解忠、恕,仁指人己物我之间没有间隔,无需推扩,自然及物;恕则需要一个推己及物的过程,二者之别仅在于自然与勉强。“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朱子指出程子说仁合忠恕之义,体用兼具。若直接以仁解一贯,反失其用意,无以见体用之分。“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将仁解一贯字,却失了体用,不得谓之一贯尔。”②在圣人分上,忠和恕相当于诚和仁,但诚、仁之间关系相隔太远,无法彼此切合;且诚、仁皆偏于本体义,未见体用相别义,忠恕则关系紧密,即本体即发用,故不可将忠恕换为诚和仁。“‘忠’字在圣人是诚,‘恕’字在圣人是仁。但说诚与仁,则说开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连续,少一个不得。”③“然曰忠曰恕,则见体用相因之意;曰诚曰仁,则皆该贯全体之谓,而无以见夫体用之分矣。”④
朱子指出忠恕正当之义乃日用为学功夫,此处借言阐发形上普遍之理,因为一贯之理无形而难言,故借学者忠恕工夫以显言之,其实是为了使学者更好理解道。“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引程子说以天道解忠、人道解恕,“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这个天人之别凸显了自然一体和人为发用之别,乃本体和发用关系,二者并无高下层次之分,“忠是自然,恕随事应接,略假人为,所以有天人之辨。”⑤它和《中庸》中“天之道、人之道”不同,《中庸》所指是本体和工夫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跃进、提升过程。
忠、恕是大本与达道的体用关系。“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忠者,尽己之心,真诚不虚,实而不假,故为道体;恕者,乃是忠之发用流行,必由此心推扩而出,方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谓道之用。“大本达道”见于《中庸》中、和的体用关系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但它与《中庸》忠恕说不同,“忠恕违道不远”乃是日用工夫义,此处忠恕是高一等说,是把忠恕本有工夫义转换成本体作用义,指本体之自然发用。“‘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①朱子强调忠恕的体用合一,不可相离,好比形影关系,有其一必有其二,本体之一即在发用之多中。“忠、恕只是体、用,便是一个物事;犹形影,要除一个除不得。……忠与恕不可相离一步。”②正因为忠恕是体用本末关系,故忠对恕具有主宰决定作用,“无忠则无恕,盖本末、体用也。”③朱子采用诸多比喻来突出忠恕的这种关系,如将忠、恕比作本根和枝叶,这可说是一种本原和派生关系,“忠是本根,恕是枝叶。”还将二者喻成印板和书的关系,表明二者乃普遍之理和分殊之理关系。朱子引小程子说,从天命不已,各正性命的角度入手,以天命不已言忠,各正性命言恕,天命不已即至诚无息,于圣人分上,此忠自是至诚不已。“‘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至于变化性命,朱子指出这正是言理一和分殊处,圣人之于天下,正如天地之于万物,皆是一心而遍注一切,物物皆具一理,人人皆有圣人之心,此心此理自然遍在,这便是圣人忠恕。“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圣人之心自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圣人之忠恕也。”④
朱子从心与事的区别来看待忠恕关系,忠在心上,恕则在事,心具众理,一心应对万事,万事皆从心发。“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①朱子还以心、事说区别不同的忠,指出心上之忠是本体,事上之忠则是工夫,前者是统体义,后者仅是具体事上义,这即是曾子忠恕之忠和谋而不忠之忠的区分,“‘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为人谋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统体;主事言者,主于事而已。”②朱子对忠信和忠恕说作了比较,指出信、恕之间存在差别,突出恕的过程含义,乃是作为本体“忠”之发用,信虽然也是忠之发用,但显示的是发用之结果,为一具体定在。以树为例,恕好比气对枝叶的贯注过程,信好比枝叶对气的接受;恕好比是行,信则好比到了目的地。“枝叶不是恕。生气流注贯枝叶底是恕。信是枝叶受生气底,恕是夹界半路来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头说。发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无忠,便无信了。”③
忠一恕贯。朱子指出忠恕即是一贯之实,一贯由忠恕得以透显,一是忠,贯是恕,忠贯恕,恕贯万事。“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贯之底注脚。”④忠、恕分别为一和贯,除此之外再无独立的一贯。“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忠恕的一理、分殊关系,是作为本体的抽象超越的普遍之理与在个别事物、日用行为中所体现出的分理关系,二者在性质上相同。一理万殊,体一用殊,皆是说明本体必须通过现实多样的作用显示出来,在表现形态上多种多样,但在理上则是同一。恕上各分殊之理即是从忠上同一本体之理所发出。“忠即是实理,忠则一理,恕则万殊。”⑤“忠恕一贯,忠在一上,恕则贯乎万物之间。只是一个一,分着便各有一个一。……恕则自忠而出,所以贯之者也。”⑥
朱子强调事上践履工夫于领悟一贯本体之重要。认为理会分殊之理是领悟理一之前提,不经过恕上分殊则不可能实现忠之理一。曾子能承当孔子点醒,悟出一贯之理,正因为曾子此前已经在事上一一理会践行过,在日用礼教诸多方面下了诸多学习之功,于分殊上尽皆知了,只是对本体尚无了悟,故闻“一贯”之语而当下有悟。其他弟子未曾下如此工夫学习,不可承当此语。而且即使没有孔子当下之点醒,曾子本人工夫所至,终能契悟。在为学功夫上,朱子反对摒弃外物而仅仅专意于内心的守约之学,突出曾子于礼上事上的探究工夫。“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论语集注·里仁》)“却是曾子件件曾做来,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践履,如何识得。”①朱子还从为学先后次序出发,指出曾子讲出理一之说已过于分明。“曾子是以言下有得,发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②
朱子喜用散钱、木片设喻,告诫弟子应象曾子那样在分殊上学习,在用上一一做工夫,本体自然有得;反之,仅空谈本体而无下手工夫,则无法真正达道。“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今人钱也不识是甚么钱,有几个孔。”③它所造成的流弊使天资高者流于空虚之佛老,低者则糊里糊涂,为自造之网所遮蔽,反倒丧失儒家重实用之义。“不愁不理会得‘一’,只愁不理会得‘贯’。理会‘贯’不得便言‘一’时,天资高者流为佛老,低者只成一团鹘突物事在这里。”④朱子极为反对工夫上的精粗说,认为理无精粗,正如水一般,田中、池中、海中水只有量的多少之别,并无质之不同,以此证明分理和一理是相同的,故在为学工夫上并无精粗之别。“圣人所以发用流行处,皆此一理,岂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⑤
“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朱子首先从圣人境界讲“一以贯之”,阐发“一以贯之”所体现的理事体用义。“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里仁》)圣人全体是理,作用出来即是理之显现。虽然呈现出的作用各不相同,然皆贯穿着同一之理,是同一下的差别,分殊中的普遍。当同一之理作用于具体事物时,就表现出一种自然差异,即理一分殊也。这个理是指天地万物共具的普遍同一之理,和它相对的则是具体特殊的事物。曾子通过持久不懈的日用工夫,达到了对具体事物分殊之理的理解,经过夫子点醒,最终了悟天地共具之理,才以“一以贯之”说表达之。①当然,朱子对理一分殊的认识主要还是从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角度着眼,以之解决以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故朱子在此将一贯之本体始终放在心上讲,突出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的关系,提出圣人心与理一,心尽万理,物我无间。
朱子新解在于将理本体与《中庸》诚本体相沟通,把圣人浑然一理与天地至诚无息说结合。天地有诚而万物得所,圣人显理而万事得当,道体具有真实自然,创生不已的特质,是天地殊异万物皆具之同理;万物各归其位,各尽其性,则是道体自然发用。据此凸显圣人一以贯之的真实存在,因为圣人在至诚意义上与天地相沟通,故能如天地本体对万物造化一般,历历可见,无处不在。“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论语集注·里仁》)朱子以一本万殊解释一以贯之,以诚为万物之本,万物为诚之用,和《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对应,皆是言理事体用的一多关系。“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论语集注·里仁》)弟子担心体用之说有分成两物之嫌,朱子认为体用一物,不可分离,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二者浑然一体。朱子还强调对于此理本体,不须多说,因为本体不可见,不可言,多说反而失其本意。“要之,‘至诚无息’一句,已自剩了。”②
忠体恕用。朱子采用程颐“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说来定义忠恕,忠即是尽己,恕即是推己。忠恕就是以己为中心对待己和他人的两种方式。忠和恕皆是从心上言,尽己和推己之己皆是指己之心。朱子对“尽己之心”的“尽”提出极高要求,认为当百分之百穷尽己心,不能有丝毫姑息和欠缺,否则就不是忠。“尽时须是十分尽得,方是尽。若七分尽得,三分未尽,也不是忠。”③至于如何尽己,就不仅是理论问题,而应当在日用事为上体验、印证,否则空说无益,反致偏离本义。朱子还从语言学角度,根据字形特点,采取《周礼疏》对忠恕的解释:“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此解更为突出了忠恕在心上的意味。朱子认为忠就是真实,“忠只是一个真实。”心中所具之理必须真实,否则无法发用出来,唯有真实,其发用才无不得当,轻重厚薄大小一一合宜,这同于《中庸》不诚无物说。批评“尽物之谓恕”说,因为恕之得名,只是推己,恕只是从尽己之忠流出,流而未尽也,“‘恕’字上着‘尽’字不得。”①
朱子引用大程子说,以仁、恕对言解忠、恕,仁指人己物我之间没有间隔,无需推扩,自然及物;恕则需要一个推己及物的过程,二者之别仅在于自然与勉强。“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朱子指出程子说仁合忠恕之义,体用兼具。若直接以仁解一贯,反失其用意,无以见体用之分。“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将仁解一贯字,却失了体用,不得谓之一贯尔。”②在圣人分上,忠和恕相当于诚和仁,但诚、仁之间关系相隔太远,无法彼此切合;且诚、仁皆偏于本体义,未见体用相别义,忠恕则关系紧密,即本体即发用,故不可将忠恕换为诚和仁。“‘忠’字在圣人是诚,‘恕’字在圣人是仁。但说诚与仁,则说开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连续,少一个不得。”③“然曰忠曰恕,则见体用相因之意;曰诚曰仁,则皆该贯全体之谓,而无以见夫体用之分矣。”④
朱子指出忠恕正当之义乃日用为学功夫,此处借言阐发形上普遍之理,因为一贯之理无形而难言,故借学者忠恕工夫以显言之,其实是为了使学者更好理解道。“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引程子说以天道解忠、人道解恕,“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这个天人之别凸显了自然一体和人为发用之别,乃本体和发用关系,二者并无高下层次之分,“忠是自然,恕随事应接,略假人为,所以有天人之辨。”⑤它和《中庸》中“天之道、人之道”不同,《中庸》所指是本体和工夫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跃进、提升过程。
忠、恕是大本与达道的体用关系。“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忠者,尽己之心,真诚不虚,实而不假,故为道体;恕者,乃是忠之发用流行,必由此心推扩而出,方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谓道之用。“大本达道”见于《中庸》中、和的体用关系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但它与《中庸》忠恕说不同,“忠恕违道不远”乃是日用工夫义,此处忠恕是高一等说,是把忠恕本有工夫义转换成本体作用义,指本体之自然发用。“‘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①朱子强调忠恕的体用合一,不可相离,好比形影关系,有其一必有其二,本体之一即在发用之多中。“忠、恕只是体、用,便是一个物事;犹形影,要除一个除不得。……忠与恕不可相离一步。”②正因为忠恕是体用本末关系,故忠对恕具有主宰决定作用,“无忠则无恕,盖本末、体用也。”③朱子采用诸多比喻来突出忠恕的这种关系,如将忠、恕比作本根和枝叶,这可说是一种本原和派生关系,“忠是本根,恕是枝叶。”还将二者喻成印板和书的关系,表明二者乃普遍之理和分殊之理关系。朱子引小程子说,从天命不已,各正性命的角度入手,以天命不已言忠,各正性命言恕,天命不已即至诚无息,于圣人分上,此忠自是至诚不已。“‘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至于变化性命,朱子指出这正是言理一和分殊处,圣人之于天下,正如天地之于万物,皆是一心而遍注一切,物物皆具一理,人人皆有圣人之心,此心此理自然遍在,这便是圣人忠恕。“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圣人之心自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圣人之忠恕也。”④
朱子从心与事的区别来看待忠恕关系,忠在心上,恕则在事,心具众理,一心应对万事,万事皆从心发。“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①朱子还以心、事说区别不同的忠,指出心上之忠是本体,事上之忠则是工夫,前者是统体义,后者仅是具体事上义,这即是曾子忠恕之忠和谋而不忠之忠的区分,“‘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为人谋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统体;主事言者,主于事而已。”②朱子对忠信和忠恕说作了比较,指出信、恕之间存在差别,突出恕的过程含义,乃是作为本体“忠”之发用,信虽然也是忠之发用,但显示的是发用之结果,为一具体定在。以树为例,恕好比气对枝叶的贯注过程,信好比枝叶对气的接受;恕好比是行,信则好比到了目的地。“枝叶不是恕。生气流注贯枝叶底是恕。信是枝叶受生气底,恕是夹界半路来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头说。发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无忠,便无信了。”③
忠一恕贯。朱子指出忠恕即是一贯之实,一贯由忠恕得以透显,一是忠,贯是恕,忠贯恕,恕贯万事。“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贯之底注脚。”④忠、恕分别为一和贯,除此之外再无独立的一贯。“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忠恕的一理、分殊关系,是作为本体的抽象超越的普遍之理与在个别事物、日用行为中所体现出的分理关系,二者在性质上相同。一理万殊,体一用殊,皆是说明本体必须通过现实多样的作用显示出来,在表现形态上多种多样,但在理上则是同一。恕上各分殊之理即是从忠上同一本体之理所发出。“忠即是实理,忠则一理,恕则万殊。”⑤“忠恕一贯,忠在一上,恕则贯乎万物之间。只是一个一,分着便各有一个一。……恕则自忠而出,所以贯之者也。”⑥
朱子强调事上践履工夫于领悟一贯本体之重要。认为理会分殊之理是领悟理一之前提,不经过恕上分殊则不可能实现忠之理一。曾子能承当孔子点醒,悟出一贯之理,正因为曾子此前已经在事上一一理会践行过,在日用礼教诸多方面下了诸多学习之功,于分殊上尽皆知了,只是对本体尚无了悟,故闻“一贯”之语而当下有悟。其他弟子未曾下如此工夫学习,不可承当此语。而且即使没有孔子当下之点醒,曾子本人工夫所至,终能契悟。在为学功夫上,朱子反对摒弃外物而仅仅专意于内心的守约之学,突出曾子于礼上事上的探究工夫。“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论语集注·里仁》)“却是曾子件件曾做来,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践履,如何识得。”①朱子还从为学先后次序出发,指出曾子讲出理一之说已过于分明。“曾子是以言下有得,发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②
朱子喜用散钱、木片设喻,告诫弟子应象曾子那样在分殊上学习,在用上一一做工夫,本体自然有得;反之,仅空谈本体而无下手工夫,则无法真正达道。“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今人钱也不识是甚么钱,有几个孔。”③它所造成的流弊使天资高者流于空虚之佛老,低者则糊里糊涂,为自造之网所遮蔽,反倒丧失儒家重实用之义。“不愁不理会得‘一’,只愁不理会得‘贯’。理会‘贯’不得便言‘一’时,天资高者流为佛老,低者只成一团鹘突物事在这里。”④朱子极为反对工夫上的精粗说,认为理无精粗,正如水一般,田中、池中、海中水只有量的多少之别,并无质之不同,以此证明分理和一理是相同的,故在为学工夫上并无精粗之别。“圣人所以发用流行处,皆此一理,岂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⑤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