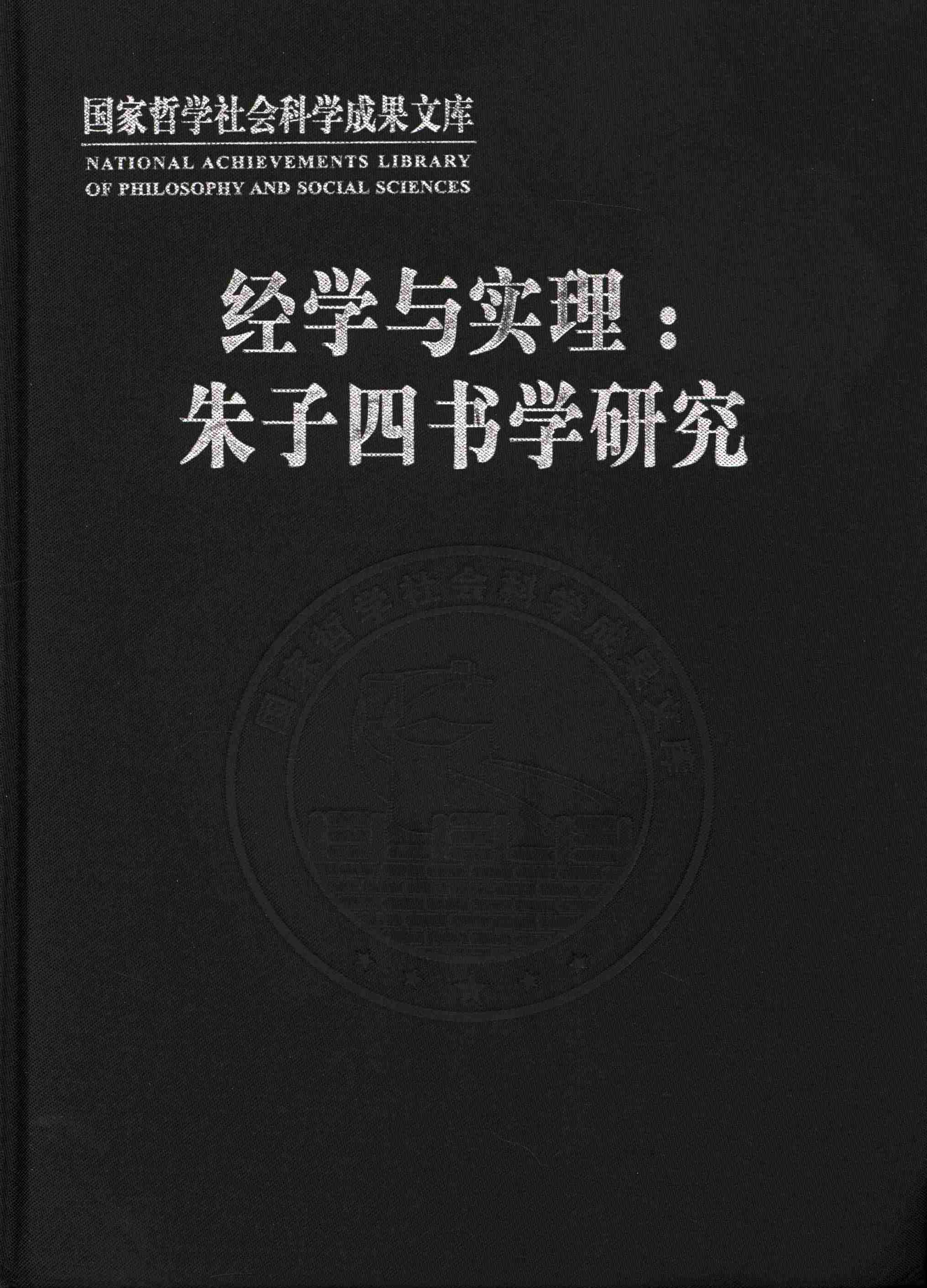三 “十六字心传”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18 |
| 颗粒名称: | 三 “十六字心传”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58-73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道统说以“十六字心传”为核心,认为儒家道统自尧舜以来一直传承至今。朱子认为,道统的核心是“允执厥中”,即通过精察人心与道心之别,达到中庸之道。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工夫。朱子强调了人心和道心的区别,并指出人心的危险和道心的微妙。他认为,只有通过精察人心和道心,才能达到中庸之道的目标。同时,朱子也强调了道统传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正确的传承方式,才能保证儒家之道的纯正性和延续性。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道统 |
内容
朱子道统说主要有两方面:传道谱系和“十六字心传”。
在道学得行的上古三代,道无需特别传扬;至道不得行之后世,则必须由专人传扬。孔门颜曾传道学宗旨,由曾氏再传至子思、孟子。在子思时代,不仅政统早已失去,连道统亦受到异端威胁。出于对道统失传的忧虑,子思写下《中庸》一书,然道传至孟子而终失其传,此后千载为异端“日新月盛”时代,特别是佛老,“弥近理而乱真”,直至二程兄弟,才通过对《中庸》的考察研读,接续子思之传,倡明圣学。然二程之说又“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朱子特别点出对二程弟子之不满,说他们所自为说“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故朱子以强烈的道统继承感,自认为二程之学的接续者,承担起阐发道统的任务。朱子道统谱系特点是越过汉唐千年岁月,将对儒学发展颇有贡献的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剔除出道统之外,认为他们没有真正领悟儒家道统之精髓,对儒家之道存在程度不同的偏离。同时,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亦没有将周敦颐、张载及他所传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列入道统。这是因为尽管朱子对道南学脉这一系抱有相当的尊敬,但是亦批评他们“静中体验未发大本”的工夫有所偏颇。尽管朱子对周敦颐、张载很是推崇,但就《四书》传道而言,二者似留意、发挥不够。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作为儒家道统说的核心,定下了道统说的基调。此一道统核心主要包括“允执厥中”的目标、“惟精惟一”的实现工夫,这一工夫之关键在于精察人心与道心之别。
朱子道统说的目标是“允执厥中”,此四字即是尧之授舜的心法,“尧当时告舜时,只说这一句”①。朱子认为,尧之授舜,本来仅此一言就“至矣,尽矣!”“舜复益之以三言者”,不过是“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即后面三言是实现“允执厥中”这个目标的方法。朱子提醒学者,执中之执为虚说,是“无执之执”,因为并没有一个作为实体的中来被人把握,“执”只是心里默自用力,不失中道。若能获得中这个天下大本,随时处中,使日用思虑动作恰到好处,那在道德成就上就达到了中庸之境。中作为一种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它表现出来就是无处而不自得,就显现为一种方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朱子认为它是舜告禹时所添入的。“后来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①这三句即表明了如何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进路。“这三句是‘允执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处。”具体而言,它有两个向度:“精”之察识与“一”之操存。在《中庸章句序》的第二段,朱子详细阐述了这一工夫过程,并对这一对概念有着详尽说明。
人心之危。心实质上只有一个,即表示价值中立、强调属性功用的虚灵知觉之心,它包括人的感性欲望和知性思考。“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虚,是心处于不作价值判断的虚空状态;灵,指心的流动不居,变化作用的活动态;知觉指心的感知、判断能力,这些皆是心所本有之特点。人心和道心则是从道德价值角度作出的区分。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指个体所必有之感性需求,其特点是“危殆而不安”,原因在于“人心易动而难反”。由形气所构成的物质躯壳为人人所私有,决定了其欲望之满足皆是不可公约的一己之私。故与此形气相连的感性欲望是危险的,容易滑向欲望的泥沼。“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②但人心之危并不代表坏,并不表示要舍去之,只是要唤醒人们对欲望之私的警惕和节制。“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个不好底根本。”正是因为形气属于个人私有,私欲、私念、私心就皆从此气而出,是一切私之根源。视身体为一切私欲的根源,是诸多学派的看法。人心对于道心而言,并非不好,其在道德价值上是中立的,可善可不善。只是因受到物欲引诱污染,人心才走向不善。朱子以圣贤亦不可无人心形气为例,说明二者并非不好,肯定了人基本需求的正当合理。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人欲才是不好,才是恶。因此,朱子特别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他指的人欲,即是人之私欲,是超出正常要求的需要。朱子对此有很明确的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③
道心之微。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构成人的超越面,指向人的价值善。特点是微妙而难见,“义理难明而易昧”。朱子认为心具道心和人心之两面,道心是义理之心,人心是血气之心。“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①道心之“微”既指精微难以捉摸,又指隐微难以发现。凡是精细之物皆隐藏在内,不易发觉显露,道心亦然。道心虽然先于人心为人所得,但人心与人的关系更为贴切,故道心往往被人心所阻隔,好比清水之混于浊水也。朱子还从人需求的三个层次来分析道心难见的原因,第一层次是生理上饥寒饱暖之类的欲望,极其明显而容易感觉,故人人皆知之;第二层次是算计谋划、趋利避害等较为精细深刻的需求,某些动物对此没法感知;第三层次是纯粹精神上的道德感受,只有人才独有,是人真正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的道心即是第三层次道德需求的反映,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故并不像反映人基本欲望的人心那样遍在呈露。“天下之物,精细底便难见,粗底便易见。饥渴寒暖是至粗底,虽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较细者言之,如利害,则禽兽已有不能知者。若是义理,则愈是难知。”②
朱子对人心和道心关系做了多角度的比较,以下观点值得重视。
人心和道心是相对性概念,判定的根据心之价值指向是理还是欲。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单独说人心,皆是好。只有当它与道心相对言时,才凸显了它不好而容易流于不正的一面。“有恁地分别说底,有不恁地说底。如单說人心,则都是好。对道心说着,便是劳攘物事,会生病痛底。”④
道心应对人心起主宰作用,即以义理为准绳来制约人欲,这样才能“允执厥中”。《中庸章句序》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构成人心的知觉欲望若没有主宰定止之物,容易放纵陷溺,危而难安;道心是义理之心,具有主宰约束功能,故可以为人心之标准。朱子用船和柁的比喻来表明道心对人心的导向作用,来自于形气之私的人心在善恶的天平上中立两可,正犹如漂荡于水中无所定向的船,必须以道心为主宰方能为善;反之,交付于形气,就失去目标和方向,则是恶。“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①朱子还从气质之心的角度论述人心可善可恶,道心则内含天理。“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②朱子认为,形气是物,道心就是则,有了公共无私之则的控制,那么形气之私就可以存在。这和胡五峰的“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是相一致的。人心和道心为所有人之共有,圣愚的差别在于以道心为主还是以人心为主。人心为人生来即有之本能,实不可无,强调人心、形气之客观存在,为人内在先天所本有,这是儒家和释老的一个区别所在。朱子指出,即便是大谈空虚之道的释老,也无法摆脱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人心终不可泯灭,且在存在上先于道心,它关乎人的现实存在。“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然则彼释迦是空虚之魁,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③
道心和人心的对立,与天理人欲、公私这两对概念相对应。道心对人心的宰制,也即是使“天理之公胜夫人欲之私。”“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④朱子在此采用二程之说,直接以天理和道心,人欲与人心画上等号。因为道心本来即含天理,人心本来即含人欲,故以理制欲,即是以道心制人心。朱子同样认为,道心与人心亦可视为公和私的关系,天理是天地万物公共之理,人不得而私;人欲则是从个体躯壳上发出的需求,为人所私有而不可公。朱子由此将人努力要达到的允执厥中的目标转换为使天理之公战胜人欲之私,即存天理灭人欲。存得一分天理,便灭得一分人欲。可见,这个人欲实质指人之私欲,并非所有欲望,合理欲望乃是不可绝灭的。“大概这两句,只是个公与私;只是一个天理,一个人欲。”⑤人心和道心本为一心,人心显明易见,道心隐晦幽闭,通过努力做工夫,可以到达道心和人心合而为一的状态。这个合而为一不是消除人心,而是使道心全部在人心上呈现,化人心为道心。于圣人而言,即是如此,圣人浑身皆是天理道心。“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都发见在那人心上。”①“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这种人心和道心的合一关系,需历经艰难的工夫实践方能达到,而且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正因为人心道心其实只是一心,上智与下愚皆兼具此二心,故圣凡之别只是在于道心与人心量的多少,而非质的差异。这就使得圣凡的差距缩短,肯定二者在人性上的同一性,许诺了即凡而圣,下学上达之可能,亦是对“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阐发。
人心与人欲。朱子哲学是复杂的思想系统,如何区分人心与人欲的关系,也是朱子思想中一个不易分清的问题。朱子在此问题上思想处于变化之中,早期采用二程的“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视人心与人欲在此语境中意义相当;后则有“‘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说,主张区别人心与人欲。但此前后期的人心与人欲的等同、区别亦是大概而论,朱子亦可能存在人心包含人欲,人欲为人心之欲望的看法,即二者类似于上下位包含关系——人心含知觉、嗜欲两面,皆其所不能无。“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大雅。②其实,在理学(朱子学)话语系统中,理与欲、理与心是相对的两组范畴,心与欲并非相对的范畴,而更多被视为一种等同关系(二程、早期朱子、阳明、甘泉)或包含关系(中晚年朱子,私欲之心、欲望之心)。故此,我们在理解朱子关于二者用语时,应保持情境、动态、相对的看法。对于朱子在具体时机下提出某种与其定见不同的说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能就此判定该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若如此处理,将导致对朱子思想成熟的复杂性、艰巨性的遮蔽。《语类》的记载,当然存在问题,编者已经标注不少说法与《集注》不相应的“问题语录”,如“记者之误”“传写之误”“记录有误”“此言盖误”“《集注》非定本”等。
以下讨论朱子的人心、人欲说。
1.滕璘辛亥(1191年)所录,朱子肯定伊川人欲人心、天理道心说。“方伯谟云:人心道心,伊川说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可学录别出。①
2.郑可学戊申(1188年)所录,朱子肯定人欲便是人心说。“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②
3.张洽癸丑(1193年)所录,朱子称赞程子人心人欲说穷尽心传之旨。“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此言尽之矣。……圣人心法无以易此。”③
正因人心即人欲,故人心之危亦可谓人欲之危。
4.“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如何谓之危?既无义理,如何不危?”黄士毅录。④
5.“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坠未坠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董铢录、潘时举录同。方子录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辞”。子静说得是。⑤
朱子去世前一年己未(1199年)吕涛所录《语录》明确提出“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⑥。可见并非人心可言危,人欲也可言危,其危表现为陷溺。这种意义下的人欲与人心相通。
第4条语录,朱子明确分别了人心、人欲、道心。朱子起首即说,“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接着以饥食寒衣之基本欲望为证,指出就通常意义而言,这种人欲并非不好,只有当它与义理相脱离的情况下才是不好。人心是心灵的知觉功能,在价值上中立,决定价值取向者在于知觉的内容,在对待的意义上,人欲与道心代表知觉的善恶两端,人心既非人欲,亦非道心,而是包含二者。就此条语录之特定语境,可知“人欲”概念包含在“人心”中,是人心的一个方面,指人心之欲望。人心与人欲并非对立,而是包容关系。故提出“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朱子屡言人只有一个心,道心、人心皆是一心所发。人欲与天理一样,皆是人心应有的必要内容。陆王之学,突出人心天理一面,完满自足。朱子更关注现实欲望对人心的腐蚀,强调道心主宰人心的功夫。朱子对人心的描述,往往就其必要欲望而言。本条语录中人欲指对饥渴等生理需要的欲求之心,对饥渴的欲求连主张四大皆空的佛学都无法否定。在朱子看来,这种欲望其实即是天理,“饮食,天理也。”朱子的理、欲范畴是在特定意义下,具体语境中相对而言,对其具体指向必须具体分析。本条语录的三句话是一个关联整体,每句各有指向,分别指向人心、人欲之心、义理之心,构筑成一个内在语义圈。第一句总说人心不能武断为不好,第二句以反问语气指出对饥寒的欲求之心符合人的正当需求,不能就此断定其为危险,意在强调此种人欲的必要合理性。第三句为第二句之补足,同样以反问语气指出即便是必要合理的欲求之心,若无义理为之主宰,难保不会走向危险之路,故必要合理的人心、人欲,也需要道德之心为其主宰。
第5条语录讨论程子的“人心,人欲”说。问者提出程子“人心,人欲”与“人心惟危”说相冲突,认为人心“恐未便是人欲”。主张人心可善可不善,人欲则全不善,二者不可等同。朱子回答切中要害,言:“人欲也未便是不好。”即人欲与人心一样,也是危而不安,不可直接称之为恶。朱子对人心与人欲关系的看法源于二程,伊川对此的经典表述是“人心,人欲;道心,天理”。分别以人欲、天理解释人心、道心。这种惟危的人心就是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应当克除之。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二程外书》卷二)①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德,一作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③
二程有的表述将“人欲”替换成“私欲”,道心表述为“正心”。这种表述更见准确,区分了此语境中的人心特指人心欲望中的私欲,此“私”不是从身体言,而是从道德上判定,此私欲“危殆”,需灭除之,以明天理。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二程遗书》卷十九)④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遗书》卷二十四)⑤
从发展眼光来看,朱子对程子人心、人欲之说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前,朱子采用二程之说,将人心与人欲、道心与天理并提。如《观心说》“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在晚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后,对二程说并未完全抛弃,而是仍有肯定。如上所引滕璘、郑可学辛亥所录、张洽癸丑所录问答,朱子皆分别以“固是”“然”“尽之矣”充分肯定程子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在与郑可学的讨论中也肯定天理道心、人心人欲分别说。朱子反复指出,人只有一个心,心是理气结合体,天理、人欲皆在此心中,皆由此心发出。心具有知觉功能,觉于理是道心,觉于欲则是人心。人欲与人心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这样就把理欲分别得很清楚,所以朱子称赞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和五峰说“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说。
晚年一般情况下,朱子对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不乏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要强调人实质上只有一个心,担心程子说分别过度,有分成两个心的嫌疑。反复指出道心与人心的分别取决于知觉的方向,觉于理是道心,觉于声色嗅味的感官欲望是人心。特别强调,以感官欲望为主的人心必不可少,也并非不好,只是危险而已。如果全是不好,则人根本无法树立道心为主的道德主体。①为此他反对“人心人欲”等同说,因为即便是圣贤上智之人,也离不开人心。如果把人心等同于人欲,就有把人心视为全部不好之意,有消除人心之意。朱子在此显然是从狭窄意义上,即与天理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人欲,认为人欲是个否定性的词,不可与人心混用。这一说法仅见于此。事实上,朱子对人心、人欲的关系存在对立或包容两种看法。当认为二者对立时,则否定人心人欲说;认为二者包容时,则肯定人心人欲说,这取决于对人心、人欲的理解。如朱子认为圣人纯是天理毫无人欲,但圣人也有满足饥渴的生理需要,此类生理欲望朱子解为人心而不是人欲。
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萧佐甲寅所闻。②
总之,对朱子人欲说应具体细致分析。当朱子单独说人欲时,人欲所指较广,在价值上中立,可善可恶,是必须而不可以消除的。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形体的存在必然有人欲,如我欲仁、饮食饥渴之类。当与天理对说时,则是狭隘义的人欲,指过分的不合理的欲望,是不应该存在的。朱子人欲说与现代人的理解存在一个很大差别,即对必要的饮食生理欲望性质的判定,需要根据其对象、数量、场合等因素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它实质上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单纯的事实概念。朱子常以天理人欲相对,学者问饮食这种人人皆有的欲望到底属于何者,朱子当即肯定,一般意义上的饮食之欲属于天理,而对于超出要求的美味等欲望,则属于人欲。其实,饮食与要求美味皆是欲望,二者差别在于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的关系。饥渴之欲本身无价值判定,决定的根据在于欲望的度,这个度需要个体根据具体情境来把握。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甘节癸丑以后所录。①
朱子常以“分数”“界限”表示此度,这个度决定了欲望的性质。就此意义而言,天理和人欲是一体的,“同行而异情”,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也有天理。只是过分了,侵占了天理的界限。故对此度数、界限需要严格把握,这也就是天理人欲的相对之意。
即便满足生存的最基本的饮食之欲,也不一定是必需的,是合理的,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场合来决定。如嗟来之食,尽管数量甚微,且为生命所必须,但必须拒绝之,以维护天理大义。由此可见,朱子的理欲观,并没有坐实具体事物,饮食等具体欲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如佛家非善非恶的“无记业”,只有当其过度或与道义发生冲突时才能做出道德善恶的判断。判定的尺度在于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故此,理欲只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其落实需要就具体情景而言。朱子有时称饥渴是人心,有时称为天理。可见,饥渴既可以是人心,人欲,也可以是天理,道心。抽象孤立的饥渴在道德上没法判断,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判断满足饥渴方式是否合宜。因此,朱子称人生只有天理,人欲是后天之物,是从天理之中产生,是对合理欲望的过度。
问:“饥食渴饮,此人心否?”曰:“然。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①沈僩戊午1198年以后所闻。
“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黄榦录。②
在《孟子集注》“养心莫善于寡欲”章,朱子同样指出耳目生理的欲望,为人所不可缺少,关键在于是否受到节制,这直接决定了本心是否受到蒙蔽。“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这个不能无的欲并不是恶,在价值上中立。总之,朱子关于人心的论述,皆是以人欲为立足点。耳目之欲为主宰则是人心,义理为主宰则是道心。故道心、人心之别亦可谓天理人欲之分。
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复杂性与他对二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的前后态度有别相关,故其后学高弟黄榦、真德秀皆强调当区别程朱人心人欲说之不同。“若辨朱程之说不可合一,则黄氏乃不易之论也。”③还指出,“欲”字单言,并无恶义,只有在天理、人欲相对时,才表示恶。而且,即便“私欲”亦非是恶。
盖“欲”字单言之,则未发善恶;七情皆未分善恶,如欲善、欲仁固皆善也。若耳目口鼻之欲,亦只是形气之私,未可以恶言。若以天理、人欲对言之,则如阴阳昼夜之相反,善恶于是判然矣。朱子“形气之私”四字,权衡轻重,允适其当,非先儒所及也。或谓私者公之反,安得不为恶?此则未然。盖所谓形气之私者,如饥食渴饮之类,皆吾形体血气所欲,岂得不谓之私?然皆人所不能无者,谓之私则可,谓之恶则未也。但以私灭公,然后为恶耳。……愚答之日,私者犹言我之所独耳,今人言私亲私恩之类是也。其可谓之恶乎?又问六经中会有谓私非恶者否?愚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如此类以恶言之,可乎?其人乃服。①
总之,朱子的人心是以知觉、欲望为主的。其人欲说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不当有的欲望。这个“人欲”是与天理对言时的特定意义,或以“私欲”出之。《集注》“人欲”说共有30余处,除一两处因行文关系外,其余皆天理、人欲对说,主旨是“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此外“人欲之私”的说法有12处。可以说,人欲在朱子那里是与天理相对立的概念,代表了否定面,与人心不可等同。但是单独言“人欲”,则并没有反面意。朱子对程子说的不满意,在于要肯定饮食等基本欲望,而不是否定。如照其人心人欲说,则饮食基本欲望无法安顿。程子说的最大问题在于道心与人心相对立,不可并存,但道心、人心却不是消灭关系,而是主导、化解关系,朱子必须给包含基本欲望的人心留一个空间,以此批评佛老之说。
惟精惟一之工夫。确保道心对人心统领的工夫落实在精察和持一上。若没有适当工夫对二者进行简别,那么将会使本来就危殆不安的人心更加危险,隐晦难见的道心更加隐晦,天理也将无法战胜人欲,道德的成就将不可能。为此,须要展开精一之功。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道德性命和生理私欲共存一体,相互夹杂。正是因为二者相即不离是人的存在之本真状态,故精心辨别二者,在知行上同时用功,谨守道心以宰制人心,以确保二者界线的不相混杂,就非常重要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困难在于危殆不安的人心时刻给予道心强大的刺激冲击,使人的行为偏离道德的轨道,造成微妙难见的道心之遮蔽;要想做到使人心受道心的约束,需要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努力修习过程。《中庸章句序》中说,“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精即是知上察识工夫,它强调精确鉴别天理人欲、道心人心,避免二者相互混杂,以保证道德的纯粹性;一即是行上操存工夫,它要求始终如一的专注于此,保持本心的中道不偏。而且,工夫不能有丝毫的间歇停顿,以便化人心之危为道心之安,使道心之隐微呈露昭彰。朱子从知行两方面分别精一之功,要求知行并进,专一用功,特别突出“惟”字的重要。朱子对精和一的范围、界线进行了划分,如学问思辨皆属于精察工夫,笃行才是唯一的行上工夫;在知上明了,还须在行上实之,才能落到实处。在精一关系上,精作为知上对善的抉择,在工夫次序上优先于行上的执持。“择善,即惟精也;固执,即惟一也。”真正做到精察的前提在于内心的“虚明安静”,排除纷杂意念的干扰,保持内心的澄澈空灵。“一”就在于内心的“诚笃确固”。朱子提出精一的知行二者乃互补互动关系。“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在惟精惟一的操作上,朱子也指出几点:其一,不仅在心上,还要在事上下工夫,工夫应贯穿于日用动静之间。他特别强调事上工夫,实处下手的重要。提出心和事的对应,即思想与行动的一致。因为道理便在日用间,所以工夫也自然在日用间,这是针对佛老工夫空虚而言的。“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①其二,因为人心道心关系极其微妙,故精一之功关键在于二者未发已发之交界处。人心和道心的差别仅仅是一条界线,二者之相互转换极为容易,稍不留意即滑向一边。由此更加强调知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只有明察了理欲之别,才有可能专守道心。“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②“人心道心,且要分别得界限分明。”③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思想的形成历经一长期过程,学界对此亦多有讨论。此一道统形成过程与朱子思想成熟相同步。简略言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拜师李侗时,注重十六字心传的政治教化义,将之视为帝王必修之学。据《壬午应诏封事》可见此时朱子道统思想尚不成熟:将尧舜禹混在一起,并没有分成两个阶段,而在《章句序》中,则说尧舜相传以“允执厥中”这一言,其他三言为舜禹相传时所补上;以《大学》致知格物和正心诚意分别解精一和执中,未能细致区分工夫和目标关系;在《章句序》中,致知仅仅属于惟精工夫,惟一属于力行工夫,而正心诚意也并非执中。“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要求孝宗“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①。
中期是在确立中和说之后,朱子对道统说有了新的认识,奠定了后来道统说的基础。朱子在辛卯(1171年)的《观心说》中提出了天理人欲,人心道心说,指出人只有一心,这些皆与他后来思想一致。但是不足处也很明显,没有提出道心和人心的来源及其特点,没有在工夫论上对精一作出分别,而且直接以心之正与不正区别人心道心,亦有不妥。“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②甲午年朱子和吴晦叔讨论人心私欲说时,反思己说“人心私欲”不对,原因在于未能察识本源,惟精惟一工夫的前提即在于知上察识本体,然后加以精一工夫。精一工夫是个长期过程,其中亦有等级进步处,并非能一蹴而就,并特别强调尧舜所谓人心私欲和常人不一样,它仅仅是稍微的走失和不自然。
后期是丁酉(1177年)朱子四书学初成,思想大体定型后,道统说亦进入完善期,此一阶段最后定见则是《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在此期间,朱子透露尧舜相传一段乃是丙午(1186年)所添入,“《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③。在早于《中庸章句序》一年的《戊申封事》中,朱子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十六字心传道统说,和《章句序》的差别仅在个别字词。如“人心、道心之别,何哉?”(《章句序》将“别”改为“异”,无“何哉”二字);“或精微而难见”。(《章句序》中改“精微”为“微妙”)。
尽管道统说为朱子所提出,但亦有其理论渊源,受二程影响尤其深。如二程提出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说,指出天人本是一体,但现实之人则存在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之别,要求以精一工夫灭弃人欲存得天理。当然,朱子道统说亦自有创见,如将《尚书》十六字心传和《中庸》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
朱子道统说常为后世诟病者,除传心说形式上近佛外,最根本的则是“十六字心传”的真伪问题。据历代学者考证,尤其是清代阎若璩的考证,证明此十六字出自《伪古文尚书》。据此似可推翻朱子所苦心经营的缘于上古的心法之说。其实不然,汉学家虽可以证实朱子所用这一条材料为伪,但是作为道统的关键,执“中”思想,的确已经在上古文献中存在。而且,朱子围绕“中”展开的儒家传道说,侧重点在于周公、孔、孟、二程,上古尧舜授受之说为后来所添入,在其中仅仅起到引子的作用,即使割弃之,其道统说亦足以成立。故否认这一段文字,并不能否定以执中为核心的道统思想,只是采用这十六个字能更好地为其理论服务而已。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是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此后儒家道统说之正统,意义重大。它是对数千年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次总结,通过对道统谱系的梳理,确定了颜曾思孟、二程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指明儒家侧重内圣之学兼顾外王之业的特点,为儒家学者提供了价值认同模式和参照标准。
在道学得行的上古三代,道无需特别传扬;至道不得行之后世,则必须由专人传扬。孔门颜曾传道学宗旨,由曾氏再传至子思、孟子。在子思时代,不仅政统早已失去,连道统亦受到异端威胁。出于对道统失传的忧虑,子思写下《中庸》一书,然道传至孟子而终失其传,此后千载为异端“日新月盛”时代,特别是佛老,“弥近理而乱真”,直至二程兄弟,才通过对《中庸》的考察研读,接续子思之传,倡明圣学。然二程之说又“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朱子特别点出对二程弟子之不满,说他们所自为说“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故朱子以强烈的道统继承感,自认为二程之学的接续者,承担起阐发道统的任务。朱子道统谱系特点是越过汉唐千年岁月,将对儒学发展颇有贡献的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剔除出道统之外,认为他们没有真正领悟儒家道统之精髓,对儒家之道存在程度不同的偏离。同时,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亦没有将周敦颐、张载及他所传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列入道统。这是因为尽管朱子对道南学脉这一系抱有相当的尊敬,但是亦批评他们“静中体验未发大本”的工夫有所偏颇。尽管朱子对周敦颐、张载很是推崇,但就《四书》传道而言,二者似留意、发挥不够。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作为儒家道统说的核心,定下了道统说的基调。此一道统核心主要包括“允执厥中”的目标、“惟精惟一”的实现工夫,这一工夫之关键在于精察人心与道心之别。
朱子道统说的目标是“允执厥中”,此四字即是尧之授舜的心法,“尧当时告舜时,只说这一句”①。朱子认为,尧之授舜,本来仅此一言就“至矣,尽矣!”“舜复益之以三言者”,不过是“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即后面三言是实现“允执厥中”这个目标的方法。朱子提醒学者,执中之执为虚说,是“无执之执”,因为并没有一个作为实体的中来被人把握,“执”只是心里默自用力,不失中道。若能获得中这个天下大本,随时处中,使日用思虑动作恰到好处,那在道德成就上就达到了中庸之境。中作为一种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它表现出来就是无处而不自得,就显现为一种方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朱子认为它是舜告禹时所添入的。“后来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①这三句即表明了如何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进路。“这三句是‘允执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处。”具体而言,它有两个向度:“精”之察识与“一”之操存。在《中庸章句序》的第二段,朱子详细阐述了这一工夫过程,并对这一对概念有着详尽说明。
人心之危。心实质上只有一个,即表示价值中立、强调属性功用的虚灵知觉之心,它包括人的感性欲望和知性思考。“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虚,是心处于不作价值判断的虚空状态;灵,指心的流动不居,变化作用的活动态;知觉指心的感知、判断能力,这些皆是心所本有之特点。人心和道心则是从道德价值角度作出的区分。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指个体所必有之感性需求,其特点是“危殆而不安”,原因在于“人心易动而难反”。由形气所构成的物质躯壳为人人所私有,决定了其欲望之满足皆是不可公约的一己之私。故与此形气相连的感性欲望是危险的,容易滑向欲望的泥沼。“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②但人心之危并不代表坏,并不表示要舍去之,只是要唤醒人们对欲望之私的警惕和节制。“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个不好底根本。”正是因为形气属于个人私有,私欲、私念、私心就皆从此气而出,是一切私之根源。视身体为一切私欲的根源,是诸多学派的看法。人心对于道心而言,并非不好,其在道德价值上是中立的,可善可不善。只是因受到物欲引诱污染,人心才走向不善。朱子以圣贤亦不可无人心形气为例,说明二者并非不好,肯定了人基本需求的正当合理。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人欲才是不好,才是恶。因此,朱子特别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他指的人欲,即是人之私欲,是超出正常要求的需要。朱子对此有很明确的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③
道心之微。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构成人的超越面,指向人的价值善。特点是微妙而难见,“义理难明而易昧”。朱子认为心具道心和人心之两面,道心是义理之心,人心是血气之心。“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①道心之“微”既指精微难以捉摸,又指隐微难以发现。凡是精细之物皆隐藏在内,不易发觉显露,道心亦然。道心虽然先于人心为人所得,但人心与人的关系更为贴切,故道心往往被人心所阻隔,好比清水之混于浊水也。朱子还从人需求的三个层次来分析道心难见的原因,第一层次是生理上饥寒饱暖之类的欲望,极其明显而容易感觉,故人人皆知之;第二层次是算计谋划、趋利避害等较为精细深刻的需求,某些动物对此没法感知;第三层次是纯粹精神上的道德感受,只有人才独有,是人真正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的道心即是第三层次道德需求的反映,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故并不像反映人基本欲望的人心那样遍在呈露。“天下之物,精细底便难见,粗底便易见。饥渴寒暖是至粗底,虽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较细者言之,如利害,则禽兽已有不能知者。若是义理,则愈是难知。”②
朱子对人心和道心关系做了多角度的比较,以下观点值得重视。
人心和道心是相对性概念,判定的根据心之价值指向是理还是欲。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单独说人心,皆是好。只有当它与道心相对言时,才凸显了它不好而容易流于不正的一面。“有恁地分别说底,有不恁地说底。如单說人心,则都是好。对道心说着,便是劳攘物事,会生病痛底。”④
道心应对人心起主宰作用,即以义理为准绳来制约人欲,这样才能“允执厥中”。《中庸章句序》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构成人心的知觉欲望若没有主宰定止之物,容易放纵陷溺,危而难安;道心是义理之心,具有主宰约束功能,故可以为人心之标准。朱子用船和柁的比喻来表明道心对人心的导向作用,来自于形气之私的人心在善恶的天平上中立两可,正犹如漂荡于水中无所定向的船,必须以道心为主宰方能为善;反之,交付于形气,就失去目标和方向,则是恶。“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①朱子还从气质之心的角度论述人心可善可恶,道心则内含天理。“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②朱子认为,形气是物,道心就是则,有了公共无私之则的控制,那么形气之私就可以存在。这和胡五峰的“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是相一致的。人心和道心为所有人之共有,圣愚的差别在于以道心为主还是以人心为主。人心为人生来即有之本能,实不可无,强调人心、形气之客观存在,为人内在先天所本有,这是儒家和释老的一个区别所在。朱子指出,即便是大谈空虚之道的释老,也无法摆脱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人心终不可泯灭,且在存在上先于道心,它关乎人的现实存在。“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然则彼释迦是空虚之魁,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③
道心和人心的对立,与天理人欲、公私这两对概念相对应。道心对人心的宰制,也即是使“天理之公胜夫人欲之私。”“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④朱子在此采用二程之说,直接以天理和道心,人欲与人心画上等号。因为道心本来即含天理,人心本来即含人欲,故以理制欲,即是以道心制人心。朱子同样认为,道心与人心亦可视为公和私的关系,天理是天地万物公共之理,人不得而私;人欲则是从个体躯壳上发出的需求,为人所私有而不可公。朱子由此将人努力要达到的允执厥中的目标转换为使天理之公战胜人欲之私,即存天理灭人欲。存得一分天理,便灭得一分人欲。可见,这个人欲实质指人之私欲,并非所有欲望,合理欲望乃是不可绝灭的。“大概这两句,只是个公与私;只是一个天理,一个人欲。”⑤人心和道心本为一心,人心显明易见,道心隐晦幽闭,通过努力做工夫,可以到达道心和人心合而为一的状态。这个合而为一不是消除人心,而是使道心全部在人心上呈现,化人心为道心。于圣人而言,即是如此,圣人浑身皆是天理道心。“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都发见在那人心上。”①“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这种人心和道心的合一关系,需历经艰难的工夫实践方能达到,而且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正因为人心道心其实只是一心,上智与下愚皆兼具此二心,故圣凡之别只是在于道心与人心量的多少,而非质的差异。这就使得圣凡的差距缩短,肯定二者在人性上的同一性,许诺了即凡而圣,下学上达之可能,亦是对“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阐发。
人心与人欲。朱子哲学是复杂的思想系统,如何区分人心与人欲的关系,也是朱子思想中一个不易分清的问题。朱子在此问题上思想处于变化之中,早期采用二程的“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视人心与人欲在此语境中意义相当;后则有“‘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说,主张区别人心与人欲。但此前后期的人心与人欲的等同、区别亦是大概而论,朱子亦可能存在人心包含人欲,人欲为人心之欲望的看法,即二者类似于上下位包含关系——人心含知觉、嗜欲两面,皆其所不能无。“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大雅。②其实,在理学(朱子学)话语系统中,理与欲、理与心是相对的两组范畴,心与欲并非相对的范畴,而更多被视为一种等同关系(二程、早期朱子、阳明、甘泉)或包含关系(中晚年朱子,私欲之心、欲望之心)。故此,我们在理解朱子关于二者用语时,应保持情境、动态、相对的看法。对于朱子在具体时机下提出某种与其定见不同的说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能就此判定该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若如此处理,将导致对朱子思想成熟的复杂性、艰巨性的遮蔽。《语类》的记载,当然存在问题,编者已经标注不少说法与《集注》不相应的“问题语录”,如“记者之误”“传写之误”“记录有误”“此言盖误”“《集注》非定本”等。
以下讨论朱子的人心、人欲说。
1.滕璘辛亥(1191年)所录,朱子肯定伊川人欲人心、天理道心说。“方伯谟云:人心道心,伊川说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可学录别出。①
2.郑可学戊申(1188年)所录,朱子肯定人欲便是人心说。“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②
3.张洽癸丑(1193年)所录,朱子称赞程子人心人欲说穷尽心传之旨。“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此言尽之矣。……圣人心法无以易此。”③
正因人心即人欲,故人心之危亦可谓人欲之危。
4.“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如何谓之危?既无义理,如何不危?”黄士毅录。④
5.“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坠未坠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董铢录、潘时举录同。方子录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辞”。子静说得是。⑤
朱子去世前一年己未(1199年)吕涛所录《语录》明确提出“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⑥。可见并非人心可言危,人欲也可言危,其危表现为陷溺。这种意义下的人欲与人心相通。
第4条语录,朱子明确分别了人心、人欲、道心。朱子起首即说,“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接着以饥食寒衣之基本欲望为证,指出就通常意义而言,这种人欲并非不好,只有当它与义理相脱离的情况下才是不好。人心是心灵的知觉功能,在价值上中立,决定价值取向者在于知觉的内容,在对待的意义上,人欲与道心代表知觉的善恶两端,人心既非人欲,亦非道心,而是包含二者。就此条语录之特定语境,可知“人欲”概念包含在“人心”中,是人心的一个方面,指人心之欲望。人心与人欲并非对立,而是包容关系。故提出“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朱子屡言人只有一个心,道心、人心皆是一心所发。人欲与天理一样,皆是人心应有的必要内容。陆王之学,突出人心天理一面,完满自足。朱子更关注现实欲望对人心的腐蚀,强调道心主宰人心的功夫。朱子对人心的描述,往往就其必要欲望而言。本条语录中人欲指对饥渴等生理需要的欲求之心,对饥渴的欲求连主张四大皆空的佛学都无法否定。在朱子看来,这种欲望其实即是天理,“饮食,天理也。”朱子的理、欲范畴是在特定意义下,具体语境中相对而言,对其具体指向必须具体分析。本条语录的三句话是一个关联整体,每句各有指向,分别指向人心、人欲之心、义理之心,构筑成一个内在语义圈。第一句总说人心不能武断为不好,第二句以反问语气指出对饥寒的欲求之心符合人的正当需求,不能就此断定其为危险,意在强调此种人欲的必要合理性。第三句为第二句之补足,同样以反问语气指出即便是必要合理的欲求之心,若无义理为之主宰,难保不会走向危险之路,故必要合理的人心、人欲,也需要道德之心为其主宰。
第5条语录讨论程子的“人心,人欲”说。问者提出程子“人心,人欲”与“人心惟危”说相冲突,认为人心“恐未便是人欲”。主张人心可善可不善,人欲则全不善,二者不可等同。朱子回答切中要害,言:“人欲也未便是不好。”即人欲与人心一样,也是危而不安,不可直接称之为恶。朱子对人心与人欲关系的看法源于二程,伊川对此的经典表述是“人心,人欲;道心,天理”。分别以人欲、天理解释人心、道心。这种惟危的人心就是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应当克除之。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二程外书》卷二)①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德,一作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③
二程有的表述将“人欲”替换成“私欲”,道心表述为“正心”。这种表述更见准确,区分了此语境中的人心特指人心欲望中的私欲,此“私”不是从身体言,而是从道德上判定,此私欲“危殆”,需灭除之,以明天理。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二程遗书》卷十九)④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遗书》卷二十四)⑤
从发展眼光来看,朱子对程子人心、人欲之说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前,朱子采用二程之说,将人心与人欲、道心与天理并提。如《观心说》“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在晚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后,对二程说并未完全抛弃,而是仍有肯定。如上所引滕璘、郑可学辛亥所录、张洽癸丑所录问答,朱子皆分别以“固是”“然”“尽之矣”充分肯定程子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在与郑可学的讨论中也肯定天理道心、人心人欲分别说。朱子反复指出,人只有一个心,心是理气结合体,天理、人欲皆在此心中,皆由此心发出。心具有知觉功能,觉于理是道心,觉于欲则是人心。人欲与人心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这样就把理欲分别得很清楚,所以朱子称赞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和五峰说“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说。
晚年一般情况下,朱子对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不乏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要强调人实质上只有一个心,担心程子说分别过度,有分成两个心的嫌疑。反复指出道心与人心的分别取决于知觉的方向,觉于理是道心,觉于声色嗅味的感官欲望是人心。特别强调,以感官欲望为主的人心必不可少,也并非不好,只是危险而已。如果全是不好,则人根本无法树立道心为主的道德主体。①为此他反对“人心人欲”等同说,因为即便是圣贤上智之人,也离不开人心。如果把人心等同于人欲,就有把人心视为全部不好之意,有消除人心之意。朱子在此显然是从狭窄意义上,即与天理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人欲,认为人欲是个否定性的词,不可与人心混用。这一说法仅见于此。事实上,朱子对人心、人欲的关系存在对立或包容两种看法。当认为二者对立时,则否定人心人欲说;认为二者包容时,则肯定人心人欲说,这取决于对人心、人欲的理解。如朱子认为圣人纯是天理毫无人欲,但圣人也有满足饥渴的生理需要,此类生理欲望朱子解为人心而不是人欲。
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萧佐甲寅所闻。②
总之,对朱子人欲说应具体细致分析。当朱子单独说人欲时,人欲所指较广,在价值上中立,可善可恶,是必须而不可以消除的。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形体的存在必然有人欲,如我欲仁、饮食饥渴之类。当与天理对说时,则是狭隘义的人欲,指过分的不合理的欲望,是不应该存在的。朱子人欲说与现代人的理解存在一个很大差别,即对必要的饮食生理欲望性质的判定,需要根据其对象、数量、场合等因素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它实质上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单纯的事实概念。朱子常以天理人欲相对,学者问饮食这种人人皆有的欲望到底属于何者,朱子当即肯定,一般意义上的饮食之欲属于天理,而对于超出要求的美味等欲望,则属于人欲。其实,饮食与要求美味皆是欲望,二者差别在于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的关系。饥渴之欲本身无价值判定,决定的根据在于欲望的度,这个度需要个体根据具体情境来把握。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甘节癸丑以后所录。①
朱子常以“分数”“界限”表示此度,这个度决定了欲望的性质。就此意义而言,天理和人欲是一体的,“同行而异情”,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也有天理。只是过分了,侵占了天理的界限。故对此度数、界限需要严格把握,这也就是天理人欲的相对之意。
即便满足生存的最基本的饮食之欲,也不一定是必需的,是合理的,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场合来决定。如嗟来之食,尽管数量甚微,且为生命所必须,但必须拒绝之,以维护天理大义。由此可见,朱子的理欲观,并没有坐实具体事物,饮食等具体欲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如佛家非善非恶的“无记业”,只有当其过度或与道义发生冲突时才能做出道德善恶的判断。判定的尺度在于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故此,理欲只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其落实需要就具体情景而言。朱子有时称饥渴是人心,有时称为天理。可见,饥渴既可以是人心,人欲,也可以是天理,道心。抽象孤立的饥渴在道德上没法判断,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判断满足饥渴方式是否合宜。因此,朱子称人生只有天理,人欲是后天之物,是从天理之中产生,是对合理欲望的过度。
问:“饥食渴饮,此人心否?”曰:“然。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①沈僩戊午1198年以后所闻。
“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黄榦录。②
在《孟子集注》“养心莫善于寡欲”章,朱子同样指出耳目生理的欲望,为人所不可缺少,关键在于是否受到节制,这直接决定了本心是否受到蒙蔽。“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这个不能无的欲并不是恶,在价值上中立。总之,朱子关于人心的论述,皆是以人欲为立足点。耳目之欲为主宰则是人心,义理为主宰则是道心。故道心、人心之别亦可谓天理人欲之分。
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复杂性与他对二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的前后态度有别相关,故其后学高弟黄榦、真德秀皆强调当区别程朱人心人欲说之不同。“若辨朱程之说不可合一,则黄氏乃不易之论也。”③还指出,“欲”字单言,并无恶义,只有在天理、人欲相对时,才表示恶。而且,即便“私欲”亦非是恶。
盖“欲”字单言之,则未发善恶;七情皆未分善恶,如欲善、欲仁固皆善也。若耳目口鼻之欲,亦只是形气之私,未可以恶言。若以天理、人欲对言之,则如阴阳昼夜之相反,善恶于是判然矣。朱子“形气之私”四字,权衡轻重,允适其当,非先儒所及也。或谓私者公之反,安得不为恶?此则未然。盖所谓形气之私者,如饥食渴饮之类,皆吾形体血气所欲,岂得不谓之私?然皆人所不能无者,谓之私则可,谓之恶则未也。但以私灭公,然后为恶耳。……愚答之日,私者犹言我之所独耳,今人言私亲私恩之类是也。其可谓之恶乎?又问六经中会有谓私非恶者否?愚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如此类以恶言之,可乎?其人乃服。①
总之,朱子的人心是以知觉、欲望为主的。其人欲说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不当有的欲望。这个“人欲”是与天理对言时的特定意义,或以“私欲”出之。《集注》“人欲”说共有30余处,除一两处因行文关系外,其余皆天理、人欲对说,主旨是“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此外“人欲之私”的说法有12处。可以说,人欲在朱子那里是与天理相对立的概念,代表了否定面,与人心不可等同。但是单独言“人欲”,则并没有反面意。朱子对程子说的不满意,在于要肯定饮食等基本欲望,而不是否定。如照其人心人欲说,则饮食基本欲望无法安顿。程子说的最大问题在于道心与人心相对立,不可并存,但道心、人心却不是消灭关系,而是主导、化解关系,朱子必须给包含基本欲望的人心留一个空间,以此批评佛老之说。
惟精惟一之工夫。确保道心对人心统领的工夫落实在精察和持一上。若没有适当工夫对二者进行简别,那么将会使本来就危殆不安的人心更加危险,隐晦难见的道心更加隐晦,天理也将无法战胜人欲,道德的成就将不可能。为此,须要展开精一之功。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道德性命和生理私欲共存一体,相互夹杂。正是因为二者相即不离是人的存在之本真状态,故精心辨别二者,在知行上同时用功,谨守道心以宰制人心,以确保二者界线的不相混杂,就非常重要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困难在于危殆不安的人心时刻给予道心强大的刺激冲击,使人的行为偏离道德的轨道,造成微妙难见的道心之遮蔽;要想做到使人心受道心的约束,需要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努力修习过程。《中庸章句序》中说,“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精即是知上察识工夫,它强调精确鉴别天理人欲、道心人心,避免二者相互混杂,以保证道德的纯粹性;一即是行上操存工夫,它要求始终如一的专注于此,保持本心的中道不偏。而且,工夫不能有丝毫的间歇停顿,以便化人心之危为道心之安,使道心之隐微呈露昭彰。朱子从知行两方面分别精一之功,要求知行并进,专一用功,特别突出“惟”字的重要。朱子对精和一的范围、界线进行了划分,如学问思辨皆属于精察工夫,笃行才是唯一的行上工夫;在知上明了,还须在行上实之,才能落到实处。在精一关系上,精作为知上对善的抉择,在工夫次序上优先于行上的执持。“择善,即惟精也;固执,即惟一也。”真正做到精察的前提在于内心的“虚明安静”,排除纷杂意念的干扰,保持内心的澄澈空灵。“一”就在于内心的“诚笃确固”。朱子提出精一的知行二者乃互补互动关系。“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在惟精惟一的操作上,朱子也指出几点:其一,不仅在心上,还要在事上下工夫,工夫应贯穿于日用动静之间。他特别强调事上工夫,实处下手的重要。提出心和事的对应,即思想与行动的一致。因为道理便在日用间,所以工夫也自然在日用间,这是针对佛老工夫空虚而言的。“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①其二,因为人心道心关系极其微妙,故精一之功关键在于二者未发已发之交界处。人心和道心的差别仅仅是一条界线,二者之相互转换极为容易,稍不留意即滑向一边。由此更加强调知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只有明察了理欲之别,才有可能专守道心。“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②“人心道心,且要分别得界限分明。”③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思想的形成历经一长期过程,学界对此亦多有讨论。此一道统形成过程与朱子思想成熟相同步。简略言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拜师李侗时,注重十六字心传的政治教化义,将之视为帝王必修之学。据《壬午应诏封事》可见此时朱子道统思想尚不成熟:将尧舜禹混在一起,并没有分成两个阶段,而在《章句序》中,则说尧舜相传以“允执厥中”这一言,其他三言为舜禹相传时所补上;以《大学》致知格物和正心诚意分别解精一和执中,未能细致区分工夫和目标关系;在《章句序》中,致知仅仅属于惟精工夫,惟一属于力行工夫,而正心诚意也并非执中。“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要求孝宗“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①。
中期是在确立中和说之后,朱子对道统说有了新的认识,奠定了后来道统说的基础。朱子在辛卯(1171年)的《观心说》中提出了天理人欲,人心道心说,指出人只有一心,这些皆与他后来思想一致。但是不足处也很明显,没有提出道心和人心的来源及其特点,没有在工夫论上对精一作出分别,而且直接以心之正与不正区别人心道心,亦有不妥。“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②甲午年朱子和吴晦叔讨论人心私欲说时,反思己说“人心私欲”不对,原因在于未能察识本源,惟精惟一工夫的前提即在于知上察识本体,然后加以精一工夫。精一工夫是个长期过程,其中亦有等级进步处,并非能一蹴而就,并特别强调尧舜所谓人心私欲和常人不一样,它仅仅是稍微的走失和不自然。
后期是丁酉(1177年)朱子四书学初成,思想大体定型后,道统说亦进入完善期,此一阶段最后定见则是《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在此期间,朱子透露尧舜相传一段乃是丙午(1186年)所添入,“《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③。在早于《中庸章句序》一年的《戊申封事》中,朱子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十六字心传道统说,和《章句序》的差别仅在个别字词。如“人心、道心之别,何哉?”(《章句序》将“别”改为“异”,无“何哉”二字);“或精微而难见”。(《章句序》中改“精微”为“微妙”)。
尽管道统说为朱子所提出,但亦有其理论渊源,受二程影响尤其深。如二程提出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说,指出天人本是一体,但现实之人则存在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之别,要求以精一工夫灭弃人欲存得天理。当然,朱子道统说亦自有创见,如将《尚书》十六字心传和《中庸》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
朱子道统说常为后世诟病者,除传心说形式上近佛外,最根本的则是“十六字心传”的真伪问题。据历代学者考证,尤其是清代阎若璩的考证,证明此十六字出自《伪古文尚书》。据此似可推翻朱子所苦心经营的缘于上古的心法之说。其实不然,汉学家虽可以证实朱子所用这一条材料为伪,但是作为道统的关键,执“中”思想,的确已经在上古文献中存在。而且,朱子围绕“中”展开的儒家传道说,侧重点在于周公、孔、孟、二程,上古尧舜授受之说为后来所添入,在其中仅仅起到引子的作用,即使割弃之,其道统说亦足以成立。故否认这一段文字,并不能否定以执中为核心的道统思想,只是采用这十六个字能更好地为其理论服务而已。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是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此后儒家道统说之正统,意义重大。它是对数千年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次总结,通过对道统谱系的梳理,确定了颜曾思孟、二程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指明儒家侧重内圣之学兼顾外王之业的特点,为儒家学者提供了价值认同模式和参照标准。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