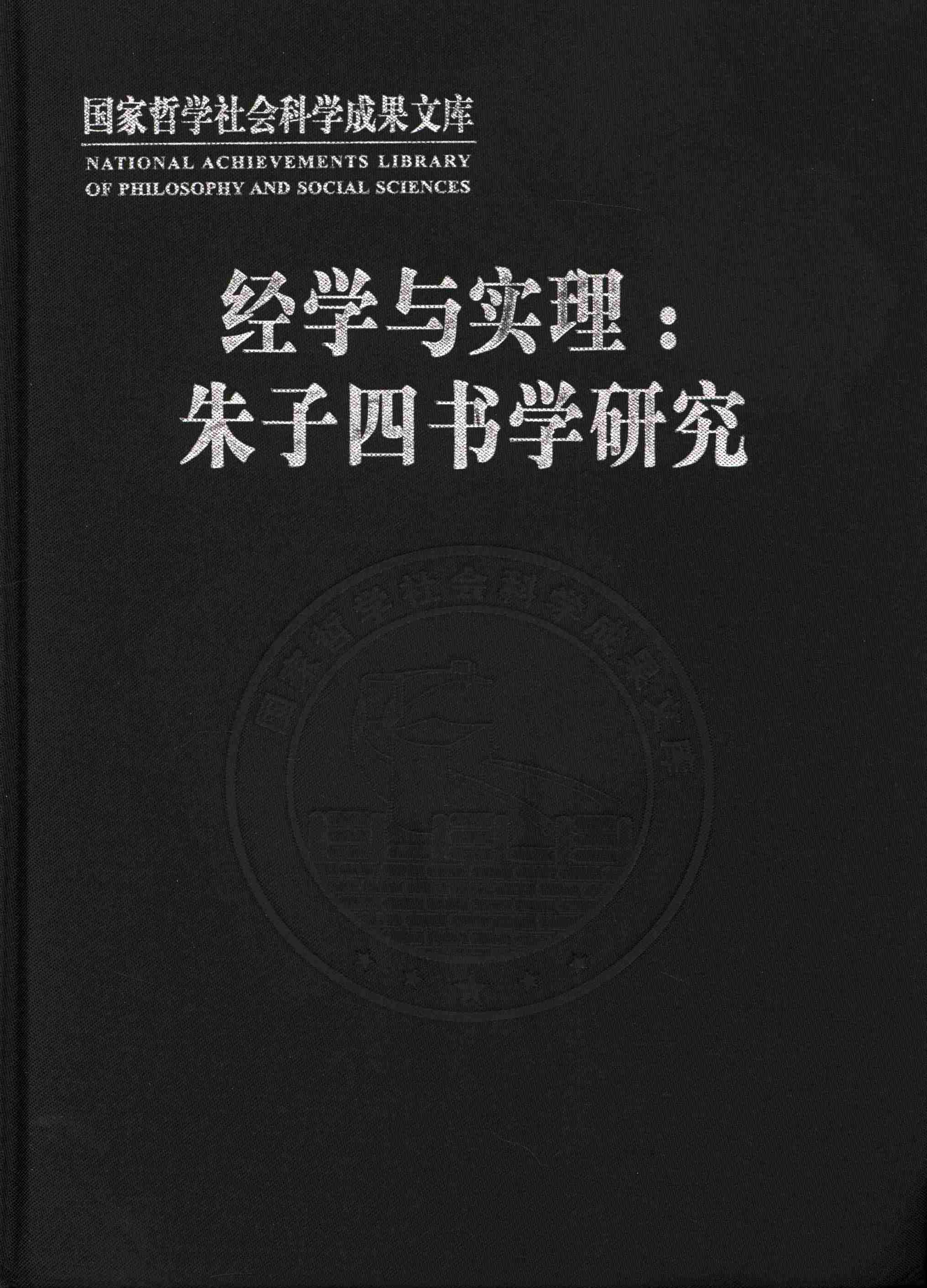第二章 朱子道统说新论
| 内容出处: |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714 |
| 颗粒名称: | 第二章 朱子道统说新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90 |
| 页码: | 54-143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子道统说新论情况的具体介绍,内容主要介绍了“十六字心传”、孔颜克复心法之传、孔曾忠恕一贯之传、道统之两翼:《四书》与《太极图说》、道统的“门户清理”等。 |
| 关键词: | 朱子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第一节 尧舜禹“十六字心传”
朱子通过对《四书》的诠释,开创了新的经学时代,即四书学时代。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功,在于赋予了四书新鲜血液,将其诠释成一个崭新的经学系统。此一新经学系统既不同于原始形态的四书,亦不同于汉唐实证背景下的经学化“四书”,而是在宋代理学大背景下孕育而出的义理化四书。此一义理化四书学内容丰富,其中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牢固树立了儒家的道统思想。朱子在四书学中提出“道统”二字并予以深刻阐发,使道统成为儒学基本范畴,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节在参考时贤成就的基础上,拟从四书学与道统、道统、学统、政统之关联、“十六字心传”、道统说之形成几个方面对朱子四书学之道统思想作一探讨。
一 四书学与道统
朱子四书学与其道统说关联甚紧,二者关系可概括为:因《四书》以明道统,明道统以率《四书》。在诠释四书的过程中,朱子提炼出道统这一创新概念,以证明儒学之道绵绵不绝,足以抗衡佛老,化民成俗。道统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四书作为传道之经这一性质的点醒。
四书学是道统说的理论来源和存在根据。从道统传道人物来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记录、传承他们思想的经典相对应,对四子思想所代表的儒学道统的理解认识,必须经由此四部经典而获得。在朱子看来,自孔孟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儒家之道蕴而不彰,没有得到有效传承,仅仅存在于言语文字之间,直至二程始从传承此道的四书中重新体悟出儒家之道并接续发扬之。由此肯定传道经典与发明儒家道统一体相关,密不可分。道统来源于圣贤之经典,亦显示出其道之有统的存在根据,故能传承越数千年之久,超越时空局限。
朱子道统思想源自对四书思想之提炼,构成贯通四书学的一条主线。表面看来,朱子道统思想取自《尚书·大禹谟》,然其实质内涵“天理”“人欲”,则为朱子四书所反复探讨之主题,其传道谱系亦早已存在于其中。如朱子说:“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①。尧命舜的“允执厥中”说《论语·尧曰》章为“允执其中”,《集注》全引杨时语以阐发孔孟传道之意:《孟子》末章,《集注》亦阐发其道统接续传承之意:
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②
朱子认为道统之传有赖于以四书为主的经典文本,经典文本在传播道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子思作《中庸》一书即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及平日所闻父师之言,以昭后之学者。故该书在“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方面,极为突出,“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这和陆九渊的心学、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悟本心相区别开来。陆九渊认为不识一个字亦可堂堂正正做个人,这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自然是可以的。但如要成为圣贤般的人物,要使个人各方面素养得到全面提升,就离不开对经典的涵养体认。二程之所以能在千年以后接续道统,也正是借助了《中庸》这部经典,“因其语而得其心也”。子思传道之功正体现于《中庸》一书,二程兄弟透过该书文字而领悟圣贤传心之妙,“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
二 道统、学统、政统
朱子提出的道统说,包蕴政统与学统之义。于朱子而言,为道、为学、为政本即通贯一体,如此方为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章句序》指出,道统之传来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上古继天立极之圣神”,此五位实为两个阶段:圣神所代表之阶段和圣王所代表之阶段。目前所能见到有经典记载者,则始于圣王尧舜。朱子为何将道统推至圣神阶段呢?学者解释其因在于伏羲的易学太极说对朱子理论体系甚有影响,但如何解释“神农、黄帝”呢?窃以为,恐怕还是为了加大道统的历史时长,树立道统的权威性,以对抗佛老。这种久远,神秘的人物,总能带给人一种神圣的崇高感。朱子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就将伏羲置于道统的源头,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这个“远”字就透露出些微消息。
道统的开启者同样是学统、政统的开启者,原因在于他们同时兼具君和师双重身份,《大学章句序》中称他们是“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故“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在那种政教合一时代,他们即是道、学、政的统一。学统是道之得以有统的必要手段,它的发展与道统紧密呼应,二者实为一皮之两面。三代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两级教学体系,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一穷正修治之道,即精一执中之道。学统之发展和道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大学章句序》说,孟氏之后,学统失传,“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学统让位于无用的记诵词章之学、无实的异端虚无之学,而且还遭受到功利权谋之说,百家无端之言的有力冲击。这些学说的纷纷涌现,使得儒学之道湮没不明,丧失了在思想界所具有的话语主导权,失其了对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即道学不明,道统失传,治道不彰,政统失效。直至在“治教休明”的宋代,二程先生才上接学统,使《大学》经传之旨复明于世。
尧舜禹汤文武是圣圣相承之过程,是道统和政统相统一时期,为儒家大道得行、内圣外王相统一时代,属于常理的“大德必得其位”。自孔子以后,转入圣师时期,德位分离,道统和政统开始脱离,故儒学转向强化道统和学统的合一。朱子认为,孔子所渴慕者仍是帝王之治,他在《论语》“何如斯可以从政”章注引尹氏说,“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①孔子不得其位并没有妨碍他的成就,他反而因继往开来之贡献越过了尧舜,孔子是以学统的形式延续了道统,他深入阐发内圣之学使道得以彰明,使借助学统形式所表现的道统依然保持了其独立性和超越性,发挥了对势的抗衡和宰制。这一抗衡是经由道统、学统领域转至对政统的重建而实现的。在这三统关系中,道统与学统密不可分,而接纳政统也一直是道统的应有之义。故《中庸章句序》即明言传道即是传政,“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诫,不过如此。”《语类》对《论语》的评价亦表露此意:“《论语》后面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之类,皆是恰好当做底事,这便是执中处。尧舜禹汤文武治天下,只是这个道理。圣门所说,也只是这个。”②朱子强调道统传至孔子是一个转折,进入“不得君师之位”的阶段。意味着道统不能再在高位顺畅下行,只能在学统的低位轨道中曲折前行,其主要任务是肃清思想界的异端庞杂之说,确立儒学在思想层面的地位。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在政治层面的抱负,而是通过道、学对君王产生影响,使之接受儒家政治标准而间接推行其外王。故此,朱子在政治上的最大主张和努力,即是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其武器即是精一执中这个道统,希望帝王接受儒家的道统说,由王而圣,恢复三代时候的圣王合一。这在朱子给皇帝的《壬午封事》、《戊申封事》中表露得极其明显。朱子与陈亮关于义利王霸之争,亦是从道统的高度来看待政统,他认为三代与汉唐的差别不在乎尽道多少这个量的问题,而是在于道之有无这个本质问题。以道观治,千五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代、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①。以此观之,这千五百年的政治与儒家之道并无多少关系。“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种偶合,其根本是功利霸道之治,于尧舜三代之王道仁义之治,根本不类,“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反诸王道之治,“莫若深考尧舜相传之心法,汤武反之之功夫,以为准则而求诸身”。②
朱子的道统说是对儒学发展的历史总结,尤其是对自宋以来儒学内部纷扰局面的整合,抵抗了佛老等对儒学的冲击破坏,指引了儒学发展方向。在北宋诸派纷争时,各家都展开过“一道德”的工作,试图统一儒家自身内部的思想,来对抗佛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朱子之前,这项工作并未完成,朱子提出道统二字即是为了作一次正本清源的工作。“道统”一名实自朱子首倡。③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朱子为何用“道”而不是“仁”或“理”这样的名称呢?孔子之学是成仁之学,一般概括为仁学而不是道学。朱子却说“子思忧虑道学失传”,采用“道学”二字,其考虑何在?④朱子用道学来概括儒家之学,一方面是看到了儒学的延续与发展、同一与差异。在孔子,道的核心为仁,工夫表现为忠恕、克己;在孟子,道的核心为仁义,工夫表现为存心、养气;而在二程,道的核心则为理,工夫表现为格物穷理,居敬涵养。更主要的一面则是“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所指包括儒家内圣外王之两面,《中庸章句序》就透露出这个道兼具道统、学统、政统的三重意味。
三 “十六字心传”
朱子道统说主要有两方面:传道谱系和“十六字心传”。
在道学得行的上古三代,道无需特别传扬;至道不得行之后世,则必须由专人传扬。孔门颜曾传道学宗旨,由曾氏再传至子思、孟子。在子思时代,不仅政统早已失去,连道统亦受到异端威胁。出于对道统失传的忧虑,子思写下《中庸》一书,然道传至孟子而终失其传,此后千载为异端“日新月盛”时代,特别是佛老,“弥近理而乱真”,直至二程兄弟,才通过对《中庸》的考察研读,接续子思之传,倡明圣学。然二程之说又“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朱子特别点出对二程弟子之不满,说他们所自为说“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故朱子以强烈的道统继承感,自认为二程之学的接续者,承担起阐发道统的任务。朱子道统谱系特点是越过汉唐千年岁月,将对儒学发展颇有贡献的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剔除出道统之外,认为他们没有真正领悟儒家道统之精髓,对儒家之道存在程度不同的偏离。同时,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亦没有将周敦颐、张载及他所传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列入道统。这是因为尽管朱子对道南学脉这一系抱有相当的尊敬,但是亦批评他们“静中体验未发大本”的工夫有所偏颇。尽管朱子对周敦颐、张载很是推崇,但就《四书》传道而言,二者似留意、发挥不够。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作为儒家道统说的核心,定下了道统说的基调。此一道统核心主要包括“允执厥中”的目标、“惟精惟一”的实现工夫,这一工夫之关键在于精察人心与道心之别。
朱子道统说的目标是“允执厥中”,此四字即是尧之授舜的心法,“尧当时告舜时,只说这一句”①。朱子认为,尧之授舜,本来仅此一言就“至矣,尽矣!”“舜复益之以三言者”,不过是“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即后面三言是实现“允执厥中”这个目标的方法。朱子提醒学者,执中之执为虚说,是“无执之执”,因为并没有一个作为实体的中来被人把握,“执”只是心里默自用力,不失中道。若能获得中这个天下大本,随时处中,使日用思虑动作恰到好处,那在道德成就上就达到了中庸之境。中作为一种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它表现出来就是无处而不自得,就显现为一种方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朱子认为它是舜告禹时所添入的。“后来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①这三句即表明了如何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进路。“这三句是‘允执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处。”具体而言,它有两个向度:“精”之察识与“一”之操存。在《中庸章句序》的第二段,朱子详细阐述了这一工夫过程,并对这一对概念有着详尽说明。
人心之危。心实质上只有一个,即表示价值中立、强调属性功用的虚灵知觉之心,它包括人的感性欲望和知性思考。“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虚,是心处于不作价值判断的虚空状态;灵,指心的流动不居,变化作用的活动态;知觉指心的感知、判断能力,这些皆是心所本有之特点。人心和道心则是从道德价值角度作出的区分。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指个体所必有之感性需求,其特点是“危殆而不安”,原因在于“人心易动而难反”。由形气所构成的物质躯壳为人人所私有,决定了其欲望之满足皆是不可公约的一己之私。故与此形气相连的感性欲望是危险的,容易滑向欲望的泥沼。“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②但人心之危并不代表坏,并不表示要舍去之,只是要唤醒人们对欲望之私的警惕和节制。“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个不好底根本。”正是因为形气属于个人私有,私欲、私念、私心就皆从此气而出,是一切私之根源。视身体为一切私欲的根源,是诸多学派的看法。人心对于道心而言,并非不好,其在道德价值上是中立的,可善可不善。只是因受到物欲引诱污染,人心才走向不善。朱子以圣贤亦不可无人心形气为例,说明二者并非不好,肯定了人基本需求的正当合理。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人欲才是不好,才是恶。因此,朱子特别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他指的人欲,即是人之私欲,是超出正常要求的需要。朱子对此有很明确的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③
道心之微。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构成人的超越面,指向人的价值善。特点是微妙而难见,“义理难明而易昧”。朱子认为心具道心和人心之两面,道心是义理之心,人心是血气之心。“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①道心之“微”既指精微难以捉摸,又指隐微难以发现。凡是精细之物皆隐藏在内,不易发觉显露,道心亦然。道心虽然先于人心为人所得,但人心与人的关系更为贴切,故道心往往被人心所阻隔,好比清水之混于浊水也。朱子还从人需求的三个层次来分析道心难见的原因,第一层次是生理上饥寒饱暖之类的欲望,极其明显而容易感觉,故人人皆知之;第二层次是算计谋划、趋利避害等较为精细深刻的需求,某些动物对此没法感知;第三层次是纯粹精神上的道德感受,只有人才独有,是人真正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的道心即是第三层次道德需求的反映,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故并不像反映人基本欲望的人心那样遍在呈露。“天下之物,精细底便难见,粗底便易见。饥渴寒暖是至粗底,虽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较细者言之,如利害,则禽兽已有不能知者。若是义理,则愈是难知。”②
朱子对人心和道心关系做了多角度的比较,以下观点值得重视。
人心和道心是相对性概念,判定的根据心之价值指向是理还是欲。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单独说人心,皆是好。只有当它与道心相对言时,才凸显了它不好而容易流于不正的一面。“有恁地分别说底,有不恁地说底。如单說人心,则都是好。对道心说着,便是劳攘物事,会生病痛底。”④
道心应对人心起主宰作用,即以义理为准绳来制约人欲,这样才能“允执厥中”。《中庸章句序》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构成人心的知觉欲望若没有主宰定止之物,容易放纵陷溺,危而难安;道心是义理之心,具有主宰约束功能,故可以为人心之标准。朱子用船和柁的比喻来表明道心对人心的导向作用,来自于形气之私的人心在善恶的天平上中立两可,正犹如漂荡于水中无所定向的船,必须以道心为主宰方能为善;反之,交付于形气,就失去目标和方向,则是恶。“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①朱子还从气质之心的角度论述人心可善可恶,道心则内含天理。“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②朱子认为,形气是物,道心就是则,有了公共无私之则的控制,那么形气之私就可以存在。这和胡五峰的“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是相一致的。人心和道心为所有人之共有,圣愚的差别在于以道心为主还是以人心为主。人心为人生来即有之本能,实不可无,强调人心、形气之客观存在,为人内在先天所本有,这是儒家和释老的一个区别所在。朱子指出,即便是大谈空虚之道的释老,也无法摆脱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人心终不可泯灭,且在存在上先于道心,它关乎人的现实存在。“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然则彼释迦是空虚之魁,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③
道心和人心的对立,与天理人欲、公私这两对概念相对应。道心对人心的宰制,也即是使“天理之公胜夫人欲之私。”“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④朱子在此采用二程之说,直接以天理和道心,人欲与人心画上等号。因为道心本来即含天理,人心本来即含人欲,故以理制欲,即是以道心制人心。朱子同样认为,道心与人心亦可视为公和私的关系,天理是天地万物公共之理,人不得而私;人欲则是从个体躯壳上发出的需求,为人所私有而不可公。朱子由此将人努力要达到的允执厥中的目标转换为使天理之公战胜人欲之私,即存天理灭人欲。存得一分天理,便灭得一分人欲。可见,这个人欲实质指人之私欲,并非所有欲望,合理欲望乃是不可绝灭的。“大概这两句,只是个公与私;只是一个天理,一个人欲。”⑤人心和道心本为一心,人心显明易见,道心隐晦幽闭,通过努力做工夫,可以到达道心和人心合而为一的状态。这个合而为一不是消除人心,而是使道心全部在人心上呈现,化人心为道心。于圣人而言,即是如此,圣人浑身皆是天理道心。“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都发见在那人心上。”①“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这种人心和道心的合一关系,需历经艰难的工夫实践方能达到,而且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正因为人心道心其实只是一心,上智与下愚皆兼具此二心,故圣凡之别只是在于道心与人心量的多少,而非质的差异。这就使得圣凡的差距缩短,肯定二者在人性上的同一性,许诺了即凡而圣,下学上达之可能,亦是对“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阐发。
人心与人欲。朱子哲学是复杂的思想系统,如何区分人心与人欲的关系,也是朱子思想中一个不易分清的问题。朱子在此问题上思想处于变化之中,早期采用二程的“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视人心与人欲在此语境中意义相当;后则有“‘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说,主张区别人心与人欲。但此前后期的人心与人欲的等同、区别亦是大概而论,朱子亦可能存在人心包含人欲,人欲为人心之欲望的看法,即二者类似于上下位包含关系——人心含知觉、嗜欲两面,皆其所不能无。“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大雅。②其实,在理学(朱子学)话语系统中,理与欲、理与心是相对的两组范畴,心与欲并非相对的范畴,而更多被视为一种等同关系(二程、早期朱子、阳明、甘泉)或包含关系(中晚年朱子,私欲之心、欲望之心)。故此,我们在理解朱子关于二者用语时,应保持情境、动态、相对的看法。对于朱子在具体时机下提出某种与其定见不同的说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能就此判定该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若如此处理,将导致对朱子思想成熟的复杂性、艰巨性的遮蔽。《语类》的记载,当然存在问题,编者已经标注不少说法与《集注》不相应的“问题语录”,如“记者之误”“传写之误”“记录有误”“此言盖误”“《集注》非定本”等。
以下讨论朱子的人心、人欲说。
1.滕璘辛亥(1191年)所录,朱子肯定伊川人欲人心、天理道心说。“方伯谟云:人心道心,伊川说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可学录别出。①
2.郑可学戊申(1188年)所录,朱子肯定人欲便是人心说。“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②
3.张洽癸丑(1193年)所录,朱子称赞程子人心人欲说穷尽心传之旨。“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此言尽之矣。……圣人心法无以易此。”③
正因人心即人欲,故人心之危亦可谓人欲之危。
4.“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如何谓之危?既无义理,如何不危?”黄士毅录。④
5.“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坠未坠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董铢录、潘时举录同。方子录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辞”。子静说得是。⑤
朱子去世前一年己未(1199年)吕涛所录《语录》明确提出“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⑥。可见并非人心可言危,人欲也可言危,其危表现为陷溺。这种意义下的人欲与人心相通。
第4条语录,朱子明确分别了人心、人欲、道心。朱子起首即说,“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接着以饥食寒衣之基本欲望为证,指出就通常意义而言,这种人欲并非不好,只有当它与义理相脱离的情况下才是不好。人心是心灵的知觉功能,在价值上中立,决定价值取向者在于知觉的内容,在对待的意义上,人欲与道心代表知觉的善恶两端,人心既非人欲,亦非道心,而是包含二者。就此条语录之特定语境,可知“人欲”概念包含在“人心”中,是人心的一个方面,指人心之欲望。人心与人欲并非对立,而是包容关系。故提出“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朱子屡言人只有一个心,道心、人心皆是一心所发。人欲与天理一样,皆是人心应有的必要内容。陆王之学,突出人心天理一面,完满自足。朱子更关注现实欲望对人心的腐蚀,强调道心主宰人心的功夫。朱子对人心的描述,往往就其必要欲望而言。本条语录中人欲指对饥渴等生理需要的欲求之心,对饥渴的欲求连主张四大皆空的佛学都无法否定。在朱子看来,这种欲望其实即是天理,“饮食,天理也。”朱子的理、欲范畴是在特定意义下,具体语境中相对而言,对其具体指向必须具体分析。本条语录的三句话是一个关联整体,每句各有指向,分别指向人心、人欲之心、义理之心,构筑成一个内在语义圈。第一句总说人心不能武断为不好,第二句以反问语气指出对饥寒的欲求之心符合人的正当需求,不能就此断定其为危险,意在强调此种人欲的必要合理性。第三句为第二句之补足,同样以反问语气指出即便是必要合理的欲求之心,若无义理为之主宰,难保不会走向危险之路,故必要合理的人心、人欲,也需要道德之心为其主宰。
第5条语录讨论程子的“人心,人欲”说。问者提出程子“人心,人欲”与“人心惟危”说相冲突,认为人心“恐未便是人欲”。主张人心可善可不善,人欲则全不善,二者不可等同。朱子回答切中要害,言:“人欲也未便是不好。”即人欲与人心一样,也是危而不安,不可直接称之为恶。朱子对人心与人欲关系的看法源于二程,伊川对此的经典表述是“人心,人欲;道心,天理”。分别以人欲、天理解释人心、道心。这种惟危的人心就是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应当克除之。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二程外书》卷二)①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德,一作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③
二程有的表述将“人欲”替换成“私欲”,道心表述为“正心”。这种表述更见准确,区分了此语境中的人心特指人心欲望中的私欲,此“私”不是从身体言,而是从道德上判定,此私欲“危殆”,需灭除之,以明天理。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二程遗书》卷十九)④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遗书》卷二十四)⑤
从发展眼光来看,朱子对程子人心、人欲之说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前,朱子采用二程之说,将人心与人欲、道心与天理并提。如《观心说》“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在晚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后,对二程说并未完全抛弃,而是仍有肯定。如上所引滕璘、郑可学辛亥所录、张洽癸丑所录问答,朱子皆分别以“固是”“然”“尽之矣”充分肯定程子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在与郑可学的讨论中也肯定天理道心、人心人欲分别说。朱子反复指出,人只有一个心,心是理气结合体,天理、人欲皆在此心中,皆由此心发出。心具有知觉功能,觉于理是道心,觉于欲则是人心。人欲与人心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这样就把理欲分别得很清楚,所以朱子称赞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和五峰说“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说。
晚年一般情况下,朱子对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不乏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要强调人实质上只有一个心,担心程子说分别过度,有分成两个心的嫌疑。反复指出道心与人心的分别取决于知觉的方向,觉于理是道心,觉于声色嗅味的感官欲望是人心。特别强调,以感官欲望为主的人心必不可少,也并非不好,只是危险而已。如果全是不好,则人根本无法树立道心为主的道德主体。①为此他反对“人心人欲”等同说,因为即便是圣贤上智之人,也离不开人心。如果把人心等同于人欲,就有把人心视为全部不好之意,有消除人心之意。朱子在此显然是从狭窄意义上,即与天理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人欲,认为人欲是个否定性的词,不可与人心混用。这一说法仅见于此。事实上,朱子对人心、人欲的关系存在对立或包容两种看法。当认为二者对立时,则否定人心人欲说;认为二者包容时,则肯定人心人欲说,这取决于对人心、人欲的理解。如朱子认为圣人纯是天理毫无人欲,但圣人也有满足饥渴的生理需要,此类生理欲望朱子解为人心而不是人欲。
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萧佐甲寅所闻。②
总之,对朱子人欲说应具体细致分析。当朱子单独说人欲时,人欲所指较广,在价值上中立,可善可恶,是必须而不可以消除的。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形体的存在必然有人欲,如我欲仁、饮食饥渴之类。当与天理对说时,则是狭隘义的人欲,指过分的不合理的欲望,是不应该存在的。朱子人欲说与现代人的理解存在一个很大差别,即对必要的饮食生理欲望性质的判定,需要根据其对象、数量、场合等因素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它实质上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单纯的事实概念。朱子常以天理人欲相对,学者问饮食这种人人皆有的欲望到底属于何者,朱子当即肯定,一般意义上的饮食之欲属于天理,而对于超出要求的美味等欲望,则属于人欲。其实,饮食与要求美味皆是欲望,二者差别在于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的关系。饥渴之欲本身无价值判定,决定的根据在于欲望的度,这个度需要个体根据具体情境来把握。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甘节癸丑以后所录。①
朱子常以“分数”“界限”表示此度,这个度决定了欲望的性质。就此意义而言,天理和人欲是一体的,“同行而异情”,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也有天理。只是过分了,侵占了天理的界限。故对此度数、界限需要严格把握,这也就是天理人欲的相对之意。
即便满足生存的最基本的饮食之欲,也不一定是必需的,是合理的,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场合来决定。如嗟来之食,尽管数量甚微,且为生命所必须,但必须拒绝之,以维护天理大义。由此可见,朱子的理欲观,并没有坐实具体事物,饮食等具体欲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如佛家非善非恶的“无记业”,只有当其过度或与道义发生冲突时才能做出道德善恶的判断。判定的尺度在于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故此,理欲只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其落实需要就具体情景而言。朱子有时称饥渴是人心,有时称为天理。可见,饥渴既可以是人心,人欲,也可以是天理,道心。抽象孤立的饥渴在道德上没法判断,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判断满足饥渴方式是否合宜。因此,朱子称人生只有天理,人欲是后天之物,是从天理之中产生,是对合理欲望的过度。
问:“饥食渴饮,此人心否?”曰:“然。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①沈僩戊午1198年以后所闻。
“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黄榦录。②
在《孟子集注》“养心莫善于寡欲”章,朱子同样指出耳目生理的欲望,为人所不可缺少,关键在于是否受到节制,这直接决定了本心是否受到蒙蔽。“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这个不能无的欲并不是恶,在价值上中立。总之,朱子关于人心的论述,皆是以人欲为立足点。耳目之欲为主宰则是人心,义理为主宰则是道心。故道心、人心之别亦可谓天理人欲之分。
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复杂性与他对二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的前后态度有别相关,故其后学高弟黄榦、真德秀皆强调当区别程朱人心人欲说之不同。“若辨朱程之说不可合一,则黄氏乃不易之论也。”③还指出,“欲”字单言,并无恶义,只有在天理、人欲相对时,才表示恶。而且,即便“私欲”亦非是恶。
盖“欲”字单言之,则未发善恶;七情皆未分善恶,如欲善、欲仁固皆善也。若耳目口鼻之欲,亦只是形气之私,未可以恶言。若以天理、人欲对言之,则如阴阳昼夜之相反,善恶于是判然矣。朱子“形气之私”四字,权衡轻重,允适其当,非先儒所及也。或谓私者公之反,安得不为恶?此则未然。盖所谓形气之私者,如饥食渴饮之类,皆吾形体血气所欲,岂得不谓之私?然皆人所不能无者,谓之私则可,谓之恶则未也。但以私灭公,然后为恶耳。……愚答之日,私者犹言我之所独耳,今人言私亲私恩之类是也。其可谓之恶乎?又问六经中会有谓私非恶者否?愚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如此类以恶言之,可乎?其人乃服。①
总之,朱子的人心是以知觉、欲望为主的。其人欲说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不当有的欲望。这个“人欲”是与天理对言时的特定意义,或以“私欲”出之。《集注》“人欲”说共有30余处,除一两处因行文关系外,其余皆天理、人欲对说,主旨是“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此外“人欲之私”的说法有12处。可以说,人欲在朱子那里是与天理相对立的概念,代表了否定面,与人心不可等同。但是单独言“人欲”,则并没有反面意。朱子对程子说的不满意,在于要肯定饮食等基本欲望,而不是否定。如照其人心人欲说,则饮食基本欲望无法安顿。程子说的最大问题在于道心与人心相对立,不可并存,但道心、人心却不是消灭关系,而是主导、化解关系,朱子必须给包含基本欲望的人心留一个空间,以此批评佛老之说。
惟精惟一之工夫。确保道心对人心统领的工夫落实在精察和持一上。若没有适当工夫对二者进行简别,那么将会使本来就危殆不安的人心更加危险,隐晦难见的道心更加隐晦,天理也将无法战胜人欲,道德的成就将不可能。为此,须要展开精一之功。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道德性命和生理私欲共存一体,相互夹杂。正是因为二者相即不离是人的存在之本真状态,故精心辨别二者,在知行上同时用功,谨守道心以宰制人心,以确保二者界线的不相混杂,就非常重要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困难在于危殆不安的人心时刻给予道心强大的刺激冲击,使人的行为偏离道德的轨道,造成微妙难见的道心之遮蔽;要想做到使人心受道心的约束,需要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努力修习过程。《中庸章句序》中说,“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精即是知上察识工夫,它强调精确鉴别天理人欲、道心人心,避免二者相互混杂,以保证道德的纯粹性;一即是行上操存工夫,它要求始终如一的专注于此,保持本心的中道不偏。而且,工夫不能有丝毫的间歇停顿,以便化人心之危为道心之安,使道心之隐微呈露昭彰。朱子从知行两方面分别精一之功,要求知行并进,专一用功,特别突出“惟”字的重要。朱子对精和一的范围、界线进行了划分,如学问思辨皆属于精察工夫,笃行才是唯一的行上工夫;在知上明了,还须在行上实之,才能落到实处。在精一关系上,精作为知上对善的抉择,在工夫次序上优先于行上的执持。“择善,即惟精也;固执,即惟一也。”真正做到精察的前提在于内心的“虚明安静”,排除纷杂意念的干扰,保持内心的澄澈空灵。“一”就在于内心的“诚笃确固”。朱子提出精一的知行二者乃互补互动关系。“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在惟精惟一的操作上,朱子也指出几点:其一,不仅在心上,还要在事上下工夫,工夫应贯穿于日用动静之间。他特别强调事上工夫,实处下手的重要。提出心和事的对应,即思想与行动的一致。因为道理便在日用间,所以工夫也自然在日用间,这是针对佛老工夫空虚而言的。“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①其二,因为人心道心关系极其微妙,故精一之功关键在于二者未发已发之交界处。人心和道心的差别仅仅是一条界线,二者之相互转换极为容易,稍不留意即滑向一边。由此更加强调知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只有明察了理欲之别,才有可能专守道心。“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②“人心道心,且要分别得界限分明。”③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思想的形成历经一长期过程,学界对此亦多有讨论。此一道统形成过程与朱子思想成熟相同步。简略言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拜师李侗时,注重十六字心传的政治教化义,将之视为帝王必修之学。据《壬午应诏封事》可见此时朱子道统思想尚不成熟:将尧舜禹混在一起,并没有分成两个阶段,而在《章句序》中,则说尧舜相传以“允执厥中”这一言,其他三言为舜禹相传时所补上;以《大学》致知格物和正心诚意分别解精一和执中,未能细致区分工夫和目标关系;在《章句序》中,致知仅仅属于惟精工夫,惟一属于力行工夫,而正心诚意也并非执中。“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要求孝宗“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①。
中期是在确立中和说之后,朱子对道统说有了新的认识,奠定了后来道统说的基础。朱子在辛卯(1171年)的《观心说》中提出了天理人欲,人心道心说,指出人只有一心,这些皆与他后来思想一致。但是不足处也很明显,没有提出道心和人心的来源及其特点,没有在工夫论上对精一作出分别,而且直接以心之正与不正区别人心道心,亦有不妥。“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②甲午年朱子和吴晦叔讨论人心私欲说时,反思己说“人心私欲”不对,原因在于未能察识本源,惟精惟一工夫的前提即在于知上察识本体,然后加以精一工夫。精一工夫是个长期过程,其中亦有等级进步处,并非能一蹴而就,并特别强调尧舜所谓人心私欲和常人不一样,它仅仅是稍微的走失和不自然。
后期是丁酉(1177年)朱子四书学初成,思想大体定型后,道统说亦进入完善期,此一阶段最后定见则是《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在此期间,朱子透露尧舜相传一段乃是丙午(1186年)所添入,“《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③。在早于《中庸章句序》一年的《戊申封事》中,朱子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十六字心传道统说,和《章句序》的差别仅在个别字词。如“人心、道心之别,何哉?”(《章句序》将“别”改为“异”,无“何哉”二字);“或精微而难见”。(《章句序》中改“精微”为“微妙”)。
尽管道统说为朱子所提出,但亦有其理论渊源,受二程影响尤其深。如二程提出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说,指出天人本是一体,但现实之人则存在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之别,要求以精一工夫灭弃人欲存得天理。当然,朱子道统说亦自有创见,如将《尚书》十六字心传和《中庸》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
朱子道统说常为后世诟病者,除传心说形式上近佛外,最根本的则是“十六字心传”的真伪问题。据历代学者考证,尤其是清代阎若璩的考证,证明此十六字出自《伪古文尚书》。据此似可推翻朱子所苦心经营的缘于上古的心法之说。其实不然,汉学家虽可以证实朱子所用这一条材料为伪,但是作为道统的关键,执“中”思想,的确已经在上古文献中存在。而且,朱子围绕“中”展开的儒家传道说,侧重点在于周公、孔、孟、二程,上古尧舜授受之说为后来所添入,在其中仅仅起到引子的作用,即使割弃之,其道统说亦足以成立。故否认这一段文字,并不能否定以执中为核心的道统思想,只是采用这十六个字能更好地为其理论服务而已。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是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此后儒家道统说之正统,意义重大。它是对数千年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次总结,通过对道统谱系的梳理,确定了颜曾思孟、二程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指明儒家侧重内圣之学兼顾外王之业的特点,为儒家学者提供了价值认同模式和参照标准。
第二节 孔颜克复心法之传
朱子道统说虽以“十六字心传”为根本,然此并非朱子道统思想之唯一表述。事实上,以颜子为代表的“克复心法”在构筑朱子道统学中亦具有其不可忽视之地位。朱子虽于《中庸章句序》言当时传孔子之道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但因颜子早逝而无著述,故其在道统中的地位多不为学者注意。有论者表达了疑惑,“道统之传未列颜渊也令人不解”。①仔细考察朱子道统说,可知颜回在道统中的地位非但未失落,反而得到有力阐明。朱子“克己复礼为仁”章注从“心法”的视角对本章作了深入阐发,指出经克己复礼工夫实现本体之仁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②故孔颜克己复礼为仁的心法授受实为“十六字心传”的重要补充。朱子道统的根本在于指明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工夫与本体实为朱子道统学不可或缺的两翼。较之“十六字心传”,孔颜“克复心法”具有无可替代之处。它既显示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同时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进路,是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朱子孔颜克复传心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具有意义。
一 “克复心法”与“十六字心传”
我们首先考察孔颜“克复心法”与“十六字心传”内涵之异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分析朱子“心法”一语的含义。朱子“心法”一语显然取自佛学(如唐末高僧黄檗希运作有《传心法要》),现代学者对朱子“传授心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一种更注重“心”与“道”的等同,将“传授心法”理解为传道之法。钱穆先生认为“所谓传授心法,义指较狭,抑且微近于禅家之所谓口传耳授密相付嘱者。……朱子实为不避此传心二字,并始畅阐传道即传心之义”①。另一种着眼于“法”,陈荣捷先生将“心法”理解为“要法”,“传授心法”即指“传授之要道”②,陈氏显然更关注“法”的切要义。朱汉民先生则将“法”理解为“术”,他认为,“所谓‘心法’,亦相当于‘心术’,即一种精神修炼的技艺或方法。”朱氏还区别了“心法”与“心传”的不同意义,认为“心传”与“道统”等同,“心法”与“工夫”“心术”等同,“心法”仅仅具有形而下的法术义,与形而上的“道”存在距离。③我们认为,“法”亦有原则、规律、道的超越意义,它兼具“道”“术”、本体与工夫两面。所谓的“十六字心传”也是指以十六字为核心的传心之法。朱子明确指出,孔颜克复为仁作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并非仅有形而下的工夫义,而是由此工夫通达于形上之仁。在整个《四书集注》中,朱子仅在《中庸章句》解题处与“颜渊问仁”处采用“心法”说,对此“心法”似不应作不同解释。朱子晚年《延和奏札》中亦将“十六字心传”与“克复心法”一并使用,皆称为“前圣相传心法”。再则,朱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作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的“切要”处正在于它更好地将工夫本体、下学上达通贯一体,此正是“克复心法”在道统中不可取代的殊胜之处。
其次,“克复”作为“克己复礼”之简称,在朱子用语中已基本固定下来,达十余次之多,且分布于各种文字。既见于朱子自著,如《四书或问》卷二,“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是以无以致其克复之功”;亦见于朱子与友朋的书信中,如《文集》卷四十四《答方伯谟》,“而从事乎克复之实”,《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而施克复之功也。”既见于与弟子论学记录中,如《语类》卷九十六,“三者也须穷理克复”;亦出于上书皇帝的重要文字,如《晦庵集》卷十一《戊申封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且“克复”之说并非朱子首倡,其前辈杨时即有此说,“颜渊克己复礼,克之己与礼一,而克复之名亡,则圣人之事也。”(《论语精义》卷六)
如上节所述,《中庸章句序》对儒家道统作了最经典之表述,涉及道统人物、传承历程、核心内容等。该序开首即表明《中庸》的使命就是传承儒学精微之道,它对道统的阐发纲举目张、烛幽阐微、透彻详尽。指出道统核心为“十六字心经”,具体又分为两层,尧舜“允执厥中”的四字相传为第一层,显示了道乃“执中”之道,学为中道之学。舜禹传承为第二层,舜禹对尧舜之道有所增益,进一步揭示了如何从工夫实现中道,若仅有一空悬“中道”本体,无实践指点工夫,道统将无法传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之所以授禹也。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该序着力阐发“惟精惟一”的工夫意义,通过“无少间断”的精察理欲,一守本心工夫,来确保“天理之公卒战胜人欲之私”,以达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之中道。
“克复心法”与《章句序》“十六字心传”有诸多相似处,相互映照。从人物谱系看,“十六字心传”是孔、颜、曾、思、孟、程子之传承路线,“克复心法”则代表了孔颜道统授受及程子之庚续。从道统核心来看,二者皆蕴含了工夫主导的思想,“十六字心传”的“精察理欲之间”与“克复心法”的“至明察其几”相对应;“一守本心之正”即仲弓敬恕存养之学,虽不如颜子克复工夫之“至健致其决”,但在最终成就上并无二致。且克己复礼作为工夫纲领之彻上彻下义,完全可以包括“精一”之学。明代朱子学者蔡清即认为“精一执中”工夫为“十六字心传”核心,精一工夫与克复工夫相对应,精察与明察、守正与健决一致。就最终实现目标来看,二者皆追求个体对“天理”本体的体悟。“十六字心传”直指天理胜人欲,道心宰人心,“克复为仁”归于“胜私欲而复于礼,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明代朱子学者蔡清即关联二者论之:
此章言圣贤传授心法。盖从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相传秘指只是一精一执中。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所谓“至明以察其机”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所谓“至健以致其决”也。(《四书蒙引》卷七)卷七
朱子晚年明确指出,两种心法相互照应支持,共同构成儒学道统。在向皇帝进言的两篇重要文字《戊申封事》《延和奏札》中,朱子皆将两种心法一并使用,可证二者实为朱子道统说之代表。《戊申封事》提出,人主之心为天下之大本,人主正心之学,见于大舜精一之传和孔子克复之教。朱子特别指出,精一、克复工夫实现正心之后,仍要归结到一身视听言动之中礼,落实到行事无过不及之执中,如此方能达到天下归仁之效用。朱子意在强调克复、精一应贯穿于心和事,这也表明朱子道统说以修身工夫为主而直达于政统。朱子将舜、孔之说先后对举,显示出舜、孔教法虽异,道之传承却一贯而下的特点。
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①
紧接着朱子以小字形式先后引出对精一之传与克复为仁的注解:
臣谨按:《尚书》舜告禹曰:“人心惟危”……又按《论语》“颜渊问仁”……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辄妄论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
此处虽未以按语形式提出克复心法说,但其意已十分鲜明。朱子在《延和奏札》五中明确提出舜禹精一、孔颜克复之学乃“心法之要”,亦是治本清源之道,进而以此批评士大夫进言皇帝之说,乃舍本求末的做法,批评功利、佛老之说乃为学之偏,君王若受其影响,则将给治理天下带来极大危害。朱子反复强调精一、克复之学作为千圣相传心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全极天理而克尽人欲,本末巨细兼包并举,告诫君王应留意舜禹精一、孔颜克复之学,在言行处事念虑之微中扩充天理,克尽人欲。
昔者舜禹、孔颜之间,盖尝病此而讲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孔子之告颜渊,既曰“克己复礼为仁”……既告之以损益四代之礼乐,而又申之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呜呼!此千圣相传心法之要。其所以极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尽者,可谓兼其本末巨细而举之矣。两汉以来,非无愿治之主,……或随世以就功名……则又不免蔽于老子浮屠之说……盖所谓千圣相传心法之要者,于是不复讲矣。……愿陛下即今日之治效,……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②不仅如此,朱子还有意强调,孔颜“克复为仁”心法较之舜禹“十六字心传”亲切紧要,孔颜授受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其作为道统之特色即在“切要”二字,“切要”体现在克复工夫与仁之本体紧密无间。朱子晚年在《玉山讲义》中特别阐发这一问题,他认为尧舜授受只是说“中、极”,到孔子才创造性地提出仁说,列圣相传之学至此方才说得亲切,此处亦见出孔子贤于尧舜。
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着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说‘中’说‘极’,今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但至孔门方说‘仁’字,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尔。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①
孔子创造性地对“仁”进行点化提升,使之上升至本体高度,同时又将其落实于人之心性,亲切易感。尧舜所传之“中、极”思想,作为超越性目标虽高明却不平实,与身心性情存在距离,学者不易当身体之。就“克复心法”与“十六字心传”相较而言,前者不仅点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工夫,而且进一步阐发了工夫如何外及于一身之视听言动,贯穿于待人接物之实事中,较之仅言“人心道心”笃实切要,平实可循。故朱子晚年于此章注释益之以程子“发明亲切”的视听言动四箴,以突出“克复”工夫的亲切紧要,要求学者于此更应深刻体悟玩味。“程子之箴,发明亲切,学者尤宜深玩”。在朱子看来,仁与克复乃“地头”与“工夫”关系,工夫与本体合为一体,克复工夫所至当下即是仁之本体,别无间隔。“克去那个,便是这个。盖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复礼’所以为仁也。仁是地头,克己复礼是工夫,所以到那地头底。”②“十六字心传”则工夫与本体明显有隔,此心传历经三代两大阶段的传承才得以完成。尧舜仅以“允执厥中”相传,突出“中”之本体而未告之以“执中”之方。至舜禹授受方才补充“执中”工夫,然仅“惟精惟一”一言,至于如何“精一”并未有说明,在指导学者用功上显然不够紧切。故在朱子看来,“克复心法”实为“十六字心传”之必要补足,元代王柏亦有见于此。他曾引此二封事中“精一”“克复”之学并举为证,指出朱子晚年以“克复为仁”章作为心法切要之言,上接尧舜禹授受的“精一”之学。
王文宪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头。朱子晚年以四箴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传。《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连举以告君而损益四代礼乐,即继于此章之后。”①
二 “心法”之两维:本体与工夫
考察“十六字心传”与“克复心法”,可知本体与工夫为朱子道统说根本问题,二者构成道统之两维,通贯一体,后世黄宗羲所言“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实可代表朱子道统说之精义。尧舜禹“十六字心传”以“中”为本体,“精一”为工夫,先言尧舜本体之“中”,继有舜禹“精一”工夫。“克复心法”则强调“克己复礼”工夫,克复工夫所至,本体之仁自然呈现,二者浑然一体。孔子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仁”本体,使古已有之的“仁”本体化,成为儒学奠基性的主题。而“十六字心传”却以“中”为根本,无法体现孔子对儒学的创造意义,使“夫子贤于尧舜”说流于空虚无力。朱子认为求道工夫虽分殊不拘一格,但却有“切要”与否之别。“十六字心传”偏重“心法”本体一面,虽提出“惟精惟一”之精察、操守工夫,然语焉未详。“克复心法”作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既以“本心之全德”解释了作为本体的仁,更突出了克复工夫之“切要”。
朱子指出孔子言仁虽多,却未曾说出仁体,个人工夫所至,方能见仁之本体。朱子基于工夫论立场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工夫特点作了创造性阐发,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刚健勇决、全面细腻、彻上彻下的“切要”特质,并引入程子四箴说作为对克复工夫之必要发挥,以便学者树立正确为学之方。因着眼工夫平实切用的特点,故朱子特别重视虚实之分,批判程门学者以“理”释“礼”、圣人安仁、万物一体释仁虚空不实,易于导致工夫躐等浮华。基于工夫笃实的考虑,在克己与复礼关系上,朱子发生了从将二者直接等同到认为二者不可等同为一的转变。朱子再三强调,克己复礼工夫的优点在于“亲切”。孔门言仁虽多,最亲切者无过于此,此处言仁与它处之别不在是否言仁之全体,而在于是否亲切。“但‘克己复礼’一句,却尤亲切。”①朱子特别突出了克复工夫刚健勇决的特色,认为此一工夫“非至健不能致其决”,并于“仲弓问仁”章中特别以按语形式,以乾坤二道作为颜、冉工夫之别来强化克复刚健无比的特色。“愚按: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朱子同时还挖掘出“克复”工夫的细腻全面性,提出“克己”指向工夫刚健有为,“复礼”则强调工夫精细全面。克复工夫的精细还体现为工夫之层次性,层层递进,循序而入,由易到难,由粗入精,工夫愈深入愈精微,乃一无穷尽无休止之追求过程。朱子特别强调克复工夫在为仁工夫中的纲要地位,认为它彻上彻下,亦深亦浅,可在最大程度上包容其他工夫。“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②夫子以克己复礼答颜子问仁,是从大纲领言,孔子对其他弟子工夫的指点,皆是从气质病痛处下手,“药病救失”,告之局部“致曲”工夫,最终落实在“克己复礼”这一工夫总纲上。“克复”作为工夫纲要体现为彻上彻下。朱子肯定克复工夫显示了颜子高明于诸弟子处,连仲弓都无法企及,可视为颜子专有,可见克复工夫的彻上性。但朱子越到晚年,则越突出克复工夫的普遍性,强调工夫的彻下。如在戊申年指出即便资质下等之人也得用克复工夫。“今‘克己复礼’一句,近下人亦用得。”③
“心法”应兼顾工夫与本体两面,也是朱子批判佛老、陆氏、浙东功利等学派的理论武器。朱子认为儒学“本末备具,不必它求”,本体工夫通贯一体。朱子由此展开两面作战,一方面既坚持本体的形上超越意义,批评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学派求末丧本,得用忘体。“本是要成物,而不及于成己。”④另一方面,朱子更强调工夫的实践日用义,着力批判张九成、陆九渊“佛学化”的心学,判定佛老与陆学高明空虚,有克己而无复礼,有“一贯”无“忠恕”。指出日用工夫不可间断,由工夫透至本体乃一长期过程,可以言说讨论,心学所主张的不可言说论,违背了圣人的一贯之道。朱子还以散钱和索串为譬,抨击陆氏的顿悟说务为高远而缺乏日用功夫,乃异端曲学,有害于学者,违背了圣人下学上达之道。
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说甚一贯。看他意思,只是拣一个笼侗底说话,将来笼罩,其实理会这个道理不得。……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①
朱、陆道统说之分歧,颇为学界所关注。朱、陆皆认可舜禹“精一”心传为儒家道统主干,但在对待“克己复礼为仁”的态度上,存在重要差异。如前所述,“克复之学”在朱子道统论中居于重要地位,陆氏则提出针对朱子的相反理解。陆氏在给胡季随信中指出克除的对象是“思索讲习”,是“讲学意见”,不仅要克除利欲私念,而且即便成圣成贤这般念头也不可有。“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②朱子发现陆子此说异常兴奋,认为抓住了断定陆氏禅学的有力证据。“因看金溪《与胡季随书》中说颜子克己处,曰:看此两行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分晓。此乃捉着真赃正贼。”③朱子反复以“克己复礼”批判陆氏,他指出意见亦当分好坏是非,不可一概除之。如成圣成贤这般好的正当念头应当有必须有,此正如人的饮食之欲,不可或缺。陆氏“除意见”说既不合圣贤之教,且误导人心,其说如同儿戏,过高而不合圣门之言。“此三字误天下学者!……某谓除去不好底意见则可,若好底意见,须是存留。”④朱子还以“克己复礼”为标准,批判陆氏“心即理”“当下就是”说,指出为学当以克己复礼作为指导工夫,从克去己私处平实下手,不可动辄“当下就是”。陆氏“心即理”说不合下学上达工夫进路,违背了夫子克己复礼之教。心即理乃克去私欲回归天理的本体状态,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而不说心即理,即是担心学者走错为学路径,故教导学者从克复之处真实用功,自可达于圣贤。
三 “克复心法”与求道历程
朱子从理论上建构儒学道统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实践上传承儒家道统。朱子本人时常透露出承担道统之愿望,如《中庸章句序》言对程子中庸之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并谦虚地表示所著《中庸章句》“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其对道统承担之意,跃然纸上。故朱子后学认为朱子乃道统之重要继承发扬者。①我们要讨论的是,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与其自身对道之实践追求存在怎样关系呢?尽管“精一之传”“克复心法”皆为朱子所肯认,但“克复心法”显然具有更为紧切的实践意味。
朱子去世前一年告诫友人,为学只有效仿颜子克复之功,方能做到知行并进,周备无缺,此实为朱子毕生工夫之写照。“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却以颜子为师,庶几足目俱到,无所欠阙。”②朱子一生求仁历程,始终贯穿克复工夫。求学延平时,延平即告以《论语》言仁皆是指点求仁之方,颜子、仲弓求仁工夫尤为得其亲切要领。“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③朱子自此确立了须于日用间克己求仁的为学宗旨。但很长一段时间,上蔡“识仁知仁”说对他影响很大。在经历中和之悟,奠定心性工夫论新规模后,朱子对上蔡观过知仁说进行了反思,于辛卯、壬辰、癸巳年间与张栻、吕祖谦等展开了仁说辩论。首先应提及的是,张栻、吕祖谦在交往中皆提醒朱子应以颜子克己工夫化除气质过于刚直的病痛。如张栻批评朱子平日处事过于豪强,“盖自它人谓为豪气底事,自学者论之只是气禀病痛,元晦所讲要学颜子,却不于此等偏处下自克之功,岂不害事。”①吕祖谦亦言朱子刚直有余、弘大温润不够,当效仿颜子,于自身气质偏处下克己工夫。“以吾丈英伟明峻之资,恐当以颜子工夫为样辙。”②在仁说辩论过程中,朱子更为重视仁的名义剖析,张、吕则反复提醒他克己工夫的重要,朱子诚恳接受之。朱子晚年也曾反思自身气质偏于忿懥。
朱子曾撰写《克己斋铭》以为自警。理学前辈多有以“克己”为斋名、铭文者,朱子唯独对程子克己四箴说推崇备至,病危临殁之时,仍请杨子直为其书写四箴用以自我提撕警醒,祛除病痛。朱子坦言对程子“四箴”的认识有一个“见其平常”到“觉其精密”的转变。此皆可证克己复礼实乃朱子一生修身工夫之指针。
欲烦为作小楷《四箴》百十字。……此箴旧见只是平常说话,近乃觉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坠云耳。……欲得妙札,时以寓目。③
去世前十二天(该书有注:此庚申闰二月二十七日书,去梦奠十二日),朱子处于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去信催问四箴之札,真正实践了生命不息,克复不止的工夫追求,此朱子所以堪为万世师表之所在也。“前书所求妙札,曾为落笔否?便中早得寄示为幸。”
从朱子对自身写照、反思文字来看,其为学追求亦是通过克复工夫以达到仁礼合一境界,特别重视通过遵守外在之礼以彰显内在之仁。《书画像自警赞》自述以礼法和仁义为用力目标,此目标正落实于克复工夫之中。“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癸巳年四十四岁所作《写照铭》称“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其工夫还是以程子四箴“制外以养其中”的克复为主旨,言“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朱子对弟子之教非常注意礼之实践,如讲解诚意章时批评陈文蔚袖角有偏。他本人晚年最大写作计划是编纂《仪礼通解》。黄榦所作《朱子行状》细致描述了朱子于视听言动诸举止上严格遵守诸礼之表现,“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特别突出了朱子临终前对礼法的恪守不渝,此足显出朱子一生求道工夫端在克己复礼也。“先生疾且革,……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蔡沉《朱文公梦奠记》所载与此不同,更强调了朱子克己复礼之精神。“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沉正之。”
四“克复心法”说的道统意义
据上述可知,“克己复礼为仁”不仅被朱子视为心法,而且是“切要”之法。“十六字心传”通过对道统历史渊源的追溯,增强儒学道统说之神秘性与历史性,以寻求更大认同,但同时也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为内容的道统被分为两个有差别的阶段:尧、舜、禹、汤、文、武圣圣相承,大道得行、内圣外王一体时代,以政统为核心;自孔子后,进入德与位,道与政相脱离时期,儒学转向了道统和学统的合一,以学统为核心。通读《章句序》全文,不难感受到,第一阶段的道统说居于中心地位,其开创性意义远远超过此后以孔子为代表之道统传承阶段,《章句序》重心皆在前两段文字中,彰显了三代君主对于道统的开创之功,孔子对道统相传之功显然相对矮化了。为此,朱子不得不刻意强调,“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但此处在道统的意义上,显然无法体现孔子“继往开来”之功要贤于尧舜开创道统之功。朱子有心推崇孔子,但实际上却不得不突出尧舜,无形中削弱了孔子,这就是朱子所面对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之贡献不在于对“中”之继承,而在于仁之创造性提升,为人的精神世界树立了大本大原。故孔子即便贤于尧舜之功,亦不可在以“中”为核心的道统上与尧舜相较。
朱子对此困境有明确认识,这从他对“中”的诠释修改中皆可看出。朱子认为“中”有两层含义:尧舜提出的无过不及的已发之中和子思提出的不偏不倚的未发之中。孔子只是继承了尧舜的已发之中说,《集注》把“尧曰”章“允执其中”的“中”注为“无过不及”即透露此点。朱子弟子辅广指出,《集注》曾经以“不偏不倚”释此“中”,后删改为“无过不及”。盖此处并非指未发之中,未发之中乃是子思首倡之,孔子此处仍是继承尧舜之说,言事上已发之中。“辅氏曰:《集注》初本并‘不偏不倚’言中,后去之而专言‘无过不及’者,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至子思而始著于书,而程子因以发中一名而含二义之说。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注》只以无过不及言中。”①元代胡炳文亦持子思发明未发之中说,“自尧舜以至夫子,所谓中者,只说‘已发之中’,而子思独提起‘未发之中’言之。……大哉斯言,真足以发千古之秘矣。”胡氏认为从尧舜到孔子谈到的“中”只是已发之中,到子思才提起未发之中说,子思的贡献在于提出未发之中,把握了中的本体义,揭发了圣学的千古奥秘所在。但此观点显然更削弱了夫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夫子对道统核心之“中”有何贡献可言?其道统地位如何能彰显呢?这的确是很值得玩味的。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说既未能彰显孔子崇高处,又导致颜回在道统中的失落,自然引发后世学者不满。但朱子从孔颜“克复为仁”之授受找到了突破点,突出了孔颜在道统上的崇高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朱子“此亦见孔子贤于尧舜”说才具有说服力。可见朱子“克复心法”说在儒家道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站在后人的立场,朱子“克复”心法之说的道统意义,尤为重要。
从历史客观性而言,孔颜授受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十六字心传”因奠基于并无确切史料根据的传说中,清儒通过证伪“十六字心传”,对此说进行了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攻击,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道统说。不管后来学者如何为“十六字心传”辩护,指出甚至撇开文献真伪,该说自有其思想意义,但如此重大思想建立于虚假材料基础上,总是大大影响了其理论说服力。如有学者已指出阎若璩“十六字心传”辨伪给理学带来的巨大冲击意义,“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还剥夺了程朱理学的经典依据,对一向以尧舜三代万世心法继承者自视的程朱理学,不啻釜底抽薪之击。”①为此,学者有意在《论语》、《尚书》关于“中”的论述外,找出《周易》有关“中”的论述,以完善儒家道统的“时中”说,印证“十六字心传”的可靠性。②而孔颜授受之儒学道统说,则将道统说奠基于极为坚实的基础上,改变了此不利局面。
此说凸显了孔子对于儒家道统的创造意义。孔子对仁的创造性提升与开拓,奠定了儒学发展的基调。他对仁的最重要阐发,即见于克己复礼为仁之说。正如朱子所认为的那样,此处方才见证了孔子贤于尧舜处,方显出孔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盖在尧舜禹所传“十六字心传”之道统中,孔子仅仅居于传承者地位,未显出其对儒学之特殊贡献。“克复心法”则充分展现了孔子以仁学对儒家道统之开创,是道统之作者而非述者。此说与后世学者不满足于仅以“述经”事业者看待孔子,推崇孔子开创之功的思想一致,古人如胡五峰、今人熊十力、牟宗三等即力推孔子仁说对道统开创之功。
“克复心法”之传以孔颜授受为标志,具有极为广阔的包容性,能最大程度容纳儒学内部各家之说,易为各家所共同接受。孔颜在儒学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威望,孔颜授受较之孔曾、孔孟等传承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能得到理学、心学、功利学派等各家之认同。儒学各派基于不同立场,对曾子、孟子学不尽表认可,但对颜子之学一致称赞而绝少异议。“学颜子之所学”为各家所共许之入道之门。史上有学者对颜渊在孔门道统中地位之被忽视甚表不满,特补充之。如明代丰坊伪造的《石经大学》在“正心”章补入“颜渊问仁”二十二字,李纪祥先生认为,“丰坊特意提出颜渊,旨在针对朱子所建立的孔、曾、思、孟道统而反对之。”③陈逢源先生亦认为丰氏此举意在“补充朱熹建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统之传中失落的环节。”此论似未注意朱子倡导“克复心法”以树立颜渊在道统中卓越地位的苦心。
近来有学者对阳明学派推崇颜子学贬低曾子学有细致论述,认为阳明学派力图通过崇颜贬曾,突出孔颜道统之传,自认接续颜子的方式来夺取程朱道统思想的话语权。①这个论断很有意思。一方面,程朱学派对颜子非常推崇,仅将颜子置于孔子一人之下。程子大力提倡“学颜子之所学”,朱子对颜子的成就有总结性论述,提出了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在“崇颜学颜”这一旗帜上程朱、阳明学派并无差别,当然在对颜子内涵的解读上,二者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两家的根本差别在于阳明学派对曾子的贬低,“贬曾”其实并非阳明学派的创见,早在宋代,陆象山、叶水心就表达了对曾子的贬低。当然,程朱学派是颜、曾一并推崇,在他们看来,即便颜曾有高下之别,也是互补而绝非对立,尤其对于学习者(教法)来说,曾子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颜子。心学一派刻意突出颜、曾的差异,自然有其思想根源,但事实表明,尽管刻意渲染颜曾的对立,阳明学派并未实现对程朱道统话语的颠覆。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看,颜、曾子并列说更为学术界所接受。
孔颜仁学授受,表明儒学道统以内圣修为之学统为根本,并不有赖于政统与治统。②而尧舜禹之“十六字心传”,含有很大的政统成分。儒家特质在心性内圣之学,理解这一点对划清儒学在未来发展中与政治之纠葛,从而在政教分离的现实社会中更好推动儒学向前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就此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许多问题,诸如新儒家所建构的内圣开出外王说是否必要?“政治儒学”是否是儒学的发展方向?生命之体证、礼乐之教化是不是对于儒学具有更紧切的意义等。
“克复心法”乃工夫与本体之结合,尤为强调工夫的意义,彰显了儒家之学以实践工夫为主的特质。这一点在朱子的孔门弟子之评中亦得到体现。如朱子认为子贡与曾子境界之别体现在知、行上,二子皆闻夫子一贯之道,“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子贡博闻强识,由知入道;曾子与之相反,于践履笃实上下工夫,由行入道。曾子实处用工,更为可行,领悟更加透彻,子贡知上工夫过多,行上不足,故对道之领悟不如曾子。朱子引尹氏说指出,“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论语集注·卫灵公》)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无工夫即无儒学,即无道统。朱子正是从工夫角度指出此心法授受更为亲切紧要,它关涉为学工夫的各个方面,彻上彻下,内外并包,不同资质者皆可循此用工以达于圣域。这点明了未来儒学之开拓发展,必须以实践工夫为支撑,否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克复心法”以工夫为本,它与以阐发本体为主的《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正好相互补充,相得愈彰。
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诠释花费了巨大心血,于晚年最终将其提升到“心法切要”的地步,作为“十六字心传”的补充与深化,体现了朱子的睿智。元代朱公迁亦认为圣贤对道统的表述存在差异,或正面表述所得道统,或间接表述道统所在,或直接承担道统,或谦虚不敢承担。孔颜克复之功,孔曾一贯之旨即正面直接表述何为道统,“愚谓圣贤或正言以叙道统之所得,或因言而见道统之所在,或直以为任,或谦不敢当,语不无少异也。其在孔门则克己复礼之功,吾道一贯之旨意乃其正言者。”①孔颜“克复心法”突出了孔颜授受在儒学道统史上不可取代的独特意义,同时发展了程颐所倡导的“学颜子之所学”的理学主题。它表明整个儒学道统的延续,皆须以孔颜之学为准的,以下学上达的工夫本体为根本路向。以现代眼光来看,“克复心法”这一以孔颜授受为标志的道统线索对儒家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工夫与本体这一主题对于儒学发展的根源性意义,指明了未来儒学之发展,应继续循此方向推扩。
第三节 孔曾忠恕一贯之传
在整部《论语》中,朱子特别重视“忠恕一贯”章,认为忠恕一贯乃儒学第一义,本章是《论语》最重要一章,对此章理解关涉到对整部《论语》的认识,亦反映出个人儒学造诣的高低。“问‘一以贯之’。曰:‘且要沉潜理会,此是《论语》中第一章。’”①朱子提出忠恕一贯章于孔门居第一义的原因在于它是孔子晚年亲传宗旨,对其他说法具有纲领性的统领意义,它道出了儒学之本体、功夫与境界,与佛老视空虚为本体、顿悟为功夫者根本不同。此宗旨自秦汉以来只有二程兄弟才接续之,二程门人亦只有谢上蔡和侯师圣于此有得。“‘一以贯之’乃圣门末后亲传密旨,其所以提纲挈领,统宗会元,盖有不可容言之妙。当时曾子黙契其意,故因门人之问,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来。则其一本万殊,脉络流通之实,益可见矣。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皆不能晓,直至二程先生始发明之。而其门人又独谢氏、侯氏为得其说。”②故朱子花费一生心血,从道之体用出发,以理一分殊注释“忠恕一贯”,阐发儒学体用思想,以此展开对其他思想的批判,在朱子经典诠释和《论语》诠释史上皆具重要意义。
一 忠一恕贯
朱子对“忠恕”章的注释以二程之说为基础,将自身看法揉入其中,阐发了忠恕体用一贯义。本章原文仅有35字,注文则多达500字,足为原文十数倍。原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③
“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朱子首先从圣人境界讲“一以贯之”,阐发“一以贯之”所体现的理事体用义。“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里仁》)圣人全体是理,作用出来即是理之显现。虽然呈现出的作用各不相同,然皆贯穿着同一之理,是同一下的差别,分殊中的普遍。当同一之理作用于具体事物时,就表现出一种自然差异,即理一分殊也。这个理是指天地万物共具的普遍同一之理,和它相对的则是具体特殊的事物。曾子通过持久不懈的日用工夫,达到了对具体事物分殊之理的理解,经过夫子点醒,最终了悟天地共具之理,才以“一以贯之”说表达之。①当然,朱子对理一分殊的认识主要还是从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角度着眼,以之解决以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故朱子在此将一贯之本体始终放在心上讲,突出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的关系,提出圣人心与理一,心尽万理,物我无间。
朱子新解在于将理本体与《中庸》诚本体相沟通,把圣人浑然一理与天地至诚无息说结合。天地有诚而万物得所,圣人显理而万事得当,道体具有真实自然,创生不已的特质,是天地殊异万物皆具之同理;万物各归其位,各尽其性,则是道体自然发用。据此凸显圣人一以贯之的真实存在,因为圣人在至诚意义上与天地相沟通,故能如天地本体对万物造化一般,历历可见,无处不在。“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论语集注·里仁》)朱子以一本万殊解释一以贯之,以诚为万物之本,万物为诚之用,和《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对应,皆是言理事体用的一多关系。“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论语集注·里仁》)弟子担心体用之说有分成两物之嫌,朱子认为体用一物,不可分离,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二者浑然一体。朱子还强调对于此理本体,不须多说,因为本体不可见,不可言,多说反而失其本意。“要之,‘至诚无息’一句,已自剩了。”②
忠体恕用。朱子采用程颐“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说来定义忠恕,忠即是尽己,恕即是推己。忠恕就是以己为中心对待己和他人的两种方式。忠和恕皆是从心上言,尽己和推己之己皆是指己之心。朱子对“尽己之心”的“尽”提出极高要求,认为当百分之百穷尽己心,不能有丝毫姑息和欠缺,否则就不是忠。“尽时须是十分尽得,方是尽。若七分尽得,三分未尽,也不是忠。”③至于如何尽己,就不仅是理论问题,而应当在日用事为上体验、印证,否则空说无益,反致偏离本义。朱子还从语言学角度,根据字形特点,采取《周礼疏》对忠恕的解释:“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此解更为突出了忠恕在心上的意味。朱子认为忠就是真实,“忠只是一个真实。”心中所具之理必须真实,否则无法发用出来,唯有真实,其发用才无不得当,轻重厚薄大小一一合宜,这同于《中庸》不诚无物说。批评“尽物之谓恕”说,因为恕之得名,只是推己,恕只是从尽己之忠流出,流而未尽也,“‘恕’字上着‘尽’字不得。”①
朱子引用大程子说,以仁、恕对言解忠、恕,仁指人己物我之间没有间隔,无需推扩,自然及物;恕则需要一个推己及物的过程,二者之别仅在于自然与勉强。“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朱子指出程子说仁合忠恕之义,体用兼具。若直接以仁解一贯,反失其用意,无以见体用之分。“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将仁解一贯字,却失了体用,不得谓之一贯尔。”②在圣人分上,忠和恕相当于诚和仁,但诚、仁之间关系相隔太远,无法彼此切合;且诚、仁皆偏于本体义,未见体用相别义,忠恕则关系紧密,即本体即发用,故不可将忠恕换为诚和仁。“‘忠’字在圣人是诚,‘恕’字在圣人是仁。但说诚与仁,则说开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连续,少一个不得。”③“然曰忠曰恕,则见体用相因之意;曰诚曰仁,则皆该贯全体之谓,而无以见夫体用之分矣。”④
朱子指出忠恕正当之义乃日用为学功夫,此处借言阐发形上普遍之理,因为一贯之理无形而难言,故借学者忠恕工夫以显言之,其实是为了使学者更好理解道。“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引程子说以天道解忠、人道解恕,“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这个天人之别凸显了自然一体和人为发用之别,乃本体和发用关系,二者并无高下层次之分,“忠是自然,恕随事应接,略假人为,所以有天人之辨。”⑤它和《中庸》中“天之道、人之道”不同,《中庸》所指是本体和工夫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跃进、提升过程。
忠、恕是大本与达道的体用关系。“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忠者,尽己之心,真诚不虚,实而不假,故为道体;恕者,乃是忠之发用流行,必由此心推扩而出,方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谓道之用。“大本达道”见于《中庸》中、和的体用关系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但它与《中庸》忠恕说不同,“忠恕违道不远”乃是日用工夫义,此处忠恕是高一等说,是把忠恕本有工夫义转换成本体作用义,指本体之自然发用。“‘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①朱子强调忠恕的体用合一,不可相离,好比形影关系,有其一必有其二,本体之一即在发用之多中。“忠、恕只是体、用,便是一个物事;犹形影,要除一个除不得。……忠与恕不可相离一步。”②正因为忠恕是体用本末关系,故忠对恕具有主宰决定作用,“无忠则无恕,盖本末、体用也。”③朱子采用诸多比喻来突出忠恕的这种关系,如将忠、恕比作本根和枝叶,这可说是一种本原和派生关系,“忠是本根,恕是枝叶。”还将二者喻成印板和书的关系,表明二者乃普遍之理和分殊之理关系。朱子引小程子说,从天命不已,各正性命的角度入手,以天命不已言忠,各正性命言恕,天命不已即至诚无息,于圣人分上,此忠自是至诚不已。“‘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至于变化性命,朱子指出这正是言理一和分殊处,圣人之于天下,正如天地之于万物,皆是一心而遍注一切,物物皆具一理,人人皆有圣人之心,此心此理自然遍在,这便是圣人忠恕。“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圣人之心自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圣人之忠恕也。”④
朱子从心与事的区别来看待忠恕关系,忠在心上,恕则在事,心具众理,一心应对万事,万事皆从心发。“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①朱子还以心、事说区别不同的忠,指出心上之忠是本体,事上之忠则是工夫,前者是统体义,后者仅是具体事上义,这即是曾子忠恕之忠和谋而不忠之忠的区分,“‘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为人谋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统体;主事言者,主于事而已。”②朱子对忠信和忠恕说作了比较,指出信、恕之间存在差别,突出恕的过程含义,乃是作为本体“忠”之发用,信虽然也是忠之发用,但显示的是发用之结果,为一具体定在。以树为例,恕好比气对枝叶的贯注过程,信好比枝叶对气的接受;恕好比是行,信则好比到了目的地。“枝叶不是恕。生气流注贯枝叶底是恕。信是枝叶受生气底,恕是夹界半路来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头说。发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无忠,便无信了。”③
忠一恕贯。朱子指出忠恕即是一贯之实,一贯由忠恕得以透显,一是忠,贯是恕,忠贯恕,恕贯万事。“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贯之底注脚。”④忠、恕分别为一和贯,除此之外再无独立的一贯。“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忠恕的一理、分殊关系,是作为本体的抽象超越的普遍之理与在个别事物、日用行为中所体现出的分理关系,二者在性质上相同。一理万殊,体一用殊,皆是说明本体必须通过现实多样的作用显示出来,在表现形态上多种多样,但在理上则是同一。恕上各分殊之理即是从忠上同一本体之理所发出。“忠即是实理,忠则一理,恕则万殊。”⑤“忠恕一贯,忠在一上,恕则贯乎万物之间。只是一个一,分着便各有一个一。……恕则自忠而出,所以贯之者也。”⑥
朱子强调事上践履工夫于领悟一贯本体之重要。认为理会分殊之理是领悟理一之前提,不经过恕上分殊则不可能实现忠之理一。曾子能承当孔子点醒,悟出一贯之理,正因为曾子此前已经在事上一一理会践行过,在日用礼教诸多方面下了诸多学习之功,于分殊上尽皆知了,只是对本体尚无了悟,故闻“一贯”之语而当下有悟。其他弟子未曾下如此工夫学习,不可承当此语。而且即使没有孔子当下之点醒,曾子本人工夫所至,终能契悟。在为学功夫上,朱子反对摒弃外物而仅仅专意于内心的守约之学,突出曾子于礼上事上的探究工夫。“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论语集注·里仁》)“却是曾子件件曾做来,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践履,如何识得。”①朱子还从为学先后次序出发,指出曾子讲出理一之说已过于分明。“曾子是以言下有得,发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②
朱子喜用散钱、木片设喻,告诫弟子应象曾子那样在分殊上学习,在用上一一做工夫,本体自然有得;反之,仅空谈本体而无下手工夫,则无法真正达道。“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今人钱也不识是甚么钱,有几个孔。”③它所造成的流弊使天资高者流于空虚之佛老,低者则糊里糊涂,为自造之网所遮蔽,反倒丧失儒家重实用之义。“不愁不理会得‘一’,只愁不理会得‘贯’。理会‘贯’不得便言‘一’时,天资高者流为佛老,低者只成一团鹘突物事在这里。”④朱子极为反对工夫上的精粗说,认为理无精粗,正如水一般,田中、池中、海中水只有量的多少之别,并无质之不同,以此证明分理和一理是相同的,故在为学工夫上并无精粗之别。“圣人所以发用流行处,皆此一理,岂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⑤
二 “一以贯之”
除曾子外,孔子亦告子贡“一以贯之”之理,“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集注·卫灵公》)朱子对此亦进行了深入阐释,指出此章主旨和“忠恕一贯”章相同,乃孔子点醒子贡儒家一贯之理,告之当从工夫上达本体,强调本体工夫的一体。此章诠释,朱子尤为注重和“忠恕一贯”的比较。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突出为学工夫的重要,朱子视积学工夫为达到一贯之理的必要前提。孔子之所以告诉子贡以一贯之理,因为子贡学问工夫已接近证悟本体,故夫子当其可而告之。朱子批评学者对此章理解不顾积学功夫而空谈一贯之理,并再次以钱和钱索为喻,证明分殊和理一不可偏废关系。
二是应将博学多识和一以贯之结合起来。在肯定博学功夫必不可少的同时,朱子指出圣人为圣,并不仅在于此,更在于体悟本体之理,贯穿于博学工夫中。今人徒有博学而未至于圣者,即在于未悟一贯之理。“今人有博学多识而不能至于圣者,只是无‘一以贯之’。然只是‘一以贯之’,而不博学多识,则又无物可贯。”①
三是较之“忠恕一贯”章,朱子对此章诠释更侧重阐发本体。此处《集注》引谢氏说突出本体自然流通贯注义和高远神妙义,认为对此本体只能意味涵养,不可言说用力。“谢氏曰:圣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观而尽识,宜其以为多学而识之也。然圣人岂务博者哉?如天之于众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贯之。’‘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论语集注·卫灵公》)朱子曾和方宾王讨论一以贯之章,方宾王以体用本末,万殊一本,一体万有之说解此,指出子贡通过致知工夫已体悟天理所在,只是未能悟出理一之妙,夫子因此点化之,证出为学之工夫于体悟天理中实不可少,朱子认同其说。
四是突出曾子、子贡入道之异和境界高低,子贡由知而入,曾子由行而入,“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论语集注·卫灵公》)在入道境界上,子贡与曾子皆闻夫子一贯之说,子贡由知上下工夫,博闻强识,由知入道;曾子恰与之相反,于践履笃实上下工夫,由行而入道。曾子从实处下手,工夫更为可行,领悟更加透彻,子贡却似乎在知上工夫过多,对道之领悟不如曾子。“尹氏曰:‘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论语集注·卫灵公》)顺此,朱子分析了颜子、曾点、子贡、曾子四人的工夫境界。颜子天资悟性高,在事上工夫极深,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子贡天资虽高,却偏于知上,日用工夫粗疏不足;曾子天资低,然而靠着刻苦工夫,于事上逐一做透,最终获得对道体领悟。曾点仅仅是知上见到理一,事上却无工夫。朱子认为一定要在具体实事上,在“贯”上实下工夫而不是凭空想象本体“一”,事上工夫到了,自然能够领会理上之一;反之,次序颠倒矣。批评仅仅想象个万殊一本重知不重行的情况,同时也批评只在分殊上做得好,却没有体验到一贯本体者,指出圣人之教,须从具体事情上知行并进,体用结合,缺一不可。“颜子聪明,事事了了。子贡聪明,工夫粗,故有阙处。曾子鲁,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来推去,事事晓得。”①
三 忠恕说的意义
三层含义。朱子认为忠恕经过层累诠释,被赋予了三层含义,第一层是程子所说天地无心之忠恕;第二层是曾子所说圣人有心无为之忠恕;第三层是《中庸》所言学者日用工夫进路之忠恕,其中学者日用工夫义之忠恕才是其本义所在。“天地是无心底忠恕,圣人是无为底忠恕,学者是求做底忠恕。”②“论著忠恕名义,自合依子思‘忠恕违道不远’是也。”③在孔子那里,其实只是说出了一贯这个本体而已,忠恕则是曾子所推出,以体用说忠恕亦是后人所言。“夫子说一贯时,未有忠恕,及曾子说忠恕时,未有体用,是后人推出来。”①忠恕的三层不同含义归结起来又只是一个忠恕而已,只是等级有差别。“皆只是这一个。学者是这个忠恕,圣人亦只是这个忠恕,天地亦只是这个忠恕。”②“其实只一个忠恕,须自看教有许多等级分明。”③朱子认为圣人全体是理,与天合一,不过天浑然一本,圣人则与物相接。圣人本体与工夫早已浑然一体,无须“尽”和“推”之工夫,故圣人头上本无忠恕,忠恕只是对学者做工夫而言。“圣人分上著忠恕字不得。”④“天地何尝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与恕。故圣人无忠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学者之事。”⑤然而,朱子同时又坚持认为,圣人亦离不开忠恕,它和学者之别在于工夫极为自然超脱,自然流出,无须推扩,学者则勉强生硬,但其最终所指向目标则是一致的。“圣人是自然底忠恕,学者是使然底忠恕。”⑥
现实批判。朱子以理一分殊说诠释忠恕一贯,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朱子以之两面作战,一方面既坚持忠恕说的形上超越意义,批评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学派求末丧本,得用忘体;同时又强调忠恕的日用工夫义,对心学的佛学化提出批评,对张九成、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及佛学进行批判,要求学者须实下功夫,本末一致。
朱子认为一贯本体须经由日用博学工夫积累而至,批评那种仅限于具体知识的掌握而不探求大本的做法,将工夫花在事为之末而没有抓住大体根本,故无法体认一贯之形上超越义。在他看来,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即有此弊,偏于博学多识而无一贯之本,未能做到下学上达的本末一体。“近见永嘉有一两相识,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那个都未有用处,却都不济事。吕伯恭向来教人亦云:‘《论语》皆虚言,不如论实事。’便要去考史。”⑦
朱子更主要的批判对象是以张九成、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及佛学思想。他批评张子韶的合人己为一贯说,认为根本不涉及人己关系,而是言工夫本体。“‘吾道一以贯之’,今人都祖张无垢说,合人己为一贯。这自是圣人说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己说得!”①他极力反对心学的顿悟本体说,指出日用工夫不可间断,不存在突然觉悟,顿觉前后皆非之事。因为由工夫透至本体存在一长期过程,可以言说讨论,心学则认为不可言说,违背了圣人的一贯之道。“今有一种学者,爱说某自某月某日有一个悟处后,便觉不同。及问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说。便是曾子传夫子一贯之道,也须可说,也须有个来历,因做甚么工夫,闻甚么说话,方能如此。”②朱子还是以散钱和索串为譬,抨击陆氏学的顿悟说务为高远而缺乏日用功夫,乃异端曲学,有害于学者,违背了圣人下学上达忠恕一贯之道。“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说甚一贯。看他意思,只是拣一个笼侗底说话,将来笼罩,其实理会这个道理不得。……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③
朱子批评学者与曾子差别在于工夫上的“虚”与“实”,学者“只得许多名字,其实不晓”,曾子是实下工夫,以真诚之心践道,对一贯之道有真实体验。“如今谁不解说‘一以贯之’!但不及曾子者,盖曾子是个实底‘一以贯之’;如今人说者,只是个虚底‘一以贯之’耳。”④学者之弊在于只是空自想象比划出一个大概意思,空知一二而无真实工夫;或徒知在事上用功而未能窥探本体。“而今学者只是想象得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实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细微紧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见得那大本。”⑤
在诠释方法上,朱子强调应注意分析、落实概念的具体含义,注意其本义与言外义,以及和其他概念的同异关系。批评浙东学派对忠恕的理解牵强附会,笼统不分,含糊不清:“今日浙中之学,正坐此弊,多强将名义比类牵合而说。要之,学者须是将许多名义如忠恕、仁义、孝弟之类,各分析区处,如经纬相似,使一一有个着落。”①批评学者将忠恕理解为不自私、不责人说在现实生活、日用工夫上皆行不通,违背了儒学宗旨。“问:“或云,忠恕只是无私己,不责人。”曰:“此说可怪。自有六经以来,不曾说不责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已,何尝说不责人!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②
四 忠恕说的形成及特点
(一)朱子对忠恕一贯的理解是一个长期的自我扬弃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几个阶段:从学延平期、初步形成期、晚年修改完善期。
从学延平时朱子就奠定了对忠恕一贯的基本看法。正是通过探究忠恕一贯,朱子才逐步厘清了儒释两家在本体与工夫上之差别,从释老之说中走出,归本伊洛之学。此时,朱子与延平、范直阁等人广泛深入的讨论忠恕说,他采用理一分殊来解释忠恕和一贯,提出二者是工夫与本体关系,当于忠恕工夫透悟一贯本体,一贯本体即在忠恕工夫中,二者不即不离。道体无处不在,曾子忠恕说乃是因门人之问道出自身对道体契悟,并指出忠恕于圣人和学者各有不同意义。“忠恕两字在圣人有圣人之用,在学者有学者之用”。圣人分上全体是一,即工夫即本体,工夫本体浑然合一,达到了体用不分,当下即是之境界,故本无须言忠恕。学者未能打通下学上达、工夫本体界限,故忠恕工夫乃是对学者而言,为学者入道之必要进路。但圣凡之别仅仅在于对本体彻悟不同,在于工夫自然纯熟不同,其进路与所至则同。下学至于上达后,自然消除了圣凡之间的界限。
因为此前虽然已“略窥大义”,然“涵泳未久,说词未莹”,故朱子还专门写有《忠恕说》。朱子《忠恕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用理一分殊阐发忠恕一贯,突出下学和上达的工夫本体关系。工夫久之自将上达本体,而彻悟本体后,平常日用将贯注本体光辉,赋予超越意义。二是人在处理世界时,最主要的是合宜处理己与物的关系,此即忠恕之道。由忠恕工夫可上达本体,而知人己物我为一。朱子特地引用二程对忠恕的定义式解释,“自其尽已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三是提出忠恕体用关系,反对脱离日用忠恕工夫而空谈一贯本体。朱子曾将此说呈给延平,延平基本认同。朱子晚年回忆此说,大体仍表满意,他认为与范直阁讨论‘忠恕’,虽然“此是三十岁以前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①朱子批评吴耕老将忠恕和一贯割裂的看法,提出忠恕即在一贯中,本体不离工夫,即工夫以显本体。
延平逝世后,朱子通过对二程及其弟子著作的研读整理,通过与湖湘学派的交流,对忠恕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一是他认为忠恕即道之全体,忠即是体,恕即是用,二者合起来体用兼具,这样来看“一贯”,方有着落,特别强调恕乃是从忠发出,不是从“一贯”流出。二是继续强调忠恕两个层面的区分,一个作为学者“入道之门、求仁之方”;一个反映圣人道体本然,忠、恕、诚、仁皆相通无隔。朱子忠恕解受程颢、谢良佐的影响极大。“示谕忠恕之说甚详,旧说似是如此。近因详看明道、上蔡诸公之说,却觉旧有病,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忠体而恕用,然后一贯之语方有落处。若言恕乃一贯发出,又却差了此意。如未深晓,且以明道、上蔡之语思之。”②此后,朱子一直坚持忠恕的体用义,提出忠实然不变而创生不已,恕则遍布天地,显露无碍,二者虽然特点各异,然却体用一源而不可析离。“近看得忠恕只是体用,其体则纯亦不已,其用则塞乎天地;其体则实然不易,其用则扩然大通。然体用一源而不可析也。”③
朱子晚年还在修改完善忠恕说。如壬子年(1192年)与郑子上讨论修改这一章,郑子上提出,今本删去前注中的“此借学者而言”将会造成下文语义不明,朱子告之并没有删去对忠恕说明的“忠也,恕也”,忠恕本来就是学者分上事。按:今本亦保留了“借学者而言”之义,改为“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还提出已经把此前“道体无二而圣人”改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这样语义就很清楚了。按:这和今本“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还是有所不同。在去世前五年的乙卯(1195年),朱子又修改了忠恕说。他告诉曾无疑忠恕本来即是学者事,与圣人其实无关,不必顾虑说得过高,忠恕可以从深浅两个层面来理解:浅言之,即日用常行之道,愚夫愚妇皆须由之,乃人立身根本处。深言之,即使圣人神通广妙,也离此忠恕不得。朱子强调忠恕虽在日用常行之中,但应有对本体之彻悟,于理上见得分明,方能赋予忠恕超越的一面。否则,仅仅限于一言一行之忠恕,未能由日用工夫把握忠恕之深层本体,将陷于拘执无用的死忠恕,只能成就个常人。“孝悌忠恕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①
朱子曾自述参究忠恕说的经过,特别提到二程的启发之功。他认为此问题关涉到对儒家本体与工夫之认识,自己能理解此章,在于将明道解释忠恕说的两段分散之语放到一起,由此悟出忠恕于学者的工夫义和圣人的本体义。否则,两重含义纠缠一起,将无法理解。朱子为此还和认同龟山之说的学者进行争论,“旧时《语录》元自分而为两,自‘以己及物’至‘违道不远是也’为一段,自‘吾道一以贯之’为一段。若只据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后云‘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自说得分明,正与‘违道不远是也’相应。”②“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为两段。后在籍溪家见,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义极完备。”③
朱子同样十分感激二程门人谢氏、侯氏说给予他的帮助启发,指出忠恕说“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
惟侯氏、谢氏晓得。”①事实上,谢、侯对此章说法甚多,不少地方都遭到朱子批评,但是在关键处予朱子莫大启发,故朱子于二人之说始终深为感激。谢、侯说哪些地方予朱子以启发呢?朱子满意于谢氏从理一分殊角度阐发忠恕说。“谢氏曰:忠恕之论,不难以训诂解,特恐学者愈不识也。且当以天地之理观之,忠譬则流而不息,恕譬则万物散殊,知此,则可以知一贯之理也。……又问忠恕之别。曰: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恕,如心而已。”②故他称赞谢氏对忠恕的理解最好,其次侯氏说和刘质夫的记录也对他颇有助益。二程其他弟子如龟山、尹氏等纠缠于《中庸》忠恕说和此处之说,而未能看穿二者含义差别。“此语是刘质夫所记,无一字错,可见质夫之学。其他诸先生如杨、尹拘于《中庸》之说,也自看明道说不曾破。谢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见未尽处。”③
(二)据上述可知,朱子主要是继承二程思想,以理一分殊之说解释忠恕一贯,认为忠恕即是一贯,朱子的这一诠解在整个《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对这一章理解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理解忠恕与道的关系。忠恕的本义是尽己推己之为学工夫,是达到道的途径,它与道是有距离的。这一点在《中庸》中有明确的说法,“忠恕违道不远”。正因如此,学者在理解曾子此说时,多受制于《中庸》说,不敢明言忠恕即是一贯之道,其中包括二程亲传弟子。朱子的突破在于接续二程说,肯定此处忠恕表达的是本体义,是一种借言,是“升一等说”,突破了《论语》、《中庸》文本之间的矛盾。他在《中庸或问》的“道不远人”章对此有具体说明,“诸家说《论语》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贯之’之义;说此章者,又引《论语》以释‘违道不远’之意,一矛一盾,终不相谋,而牵合不置,学者盖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谓‘动以天者’,然后知二者之为忠恕,其迹虽同,而所以为忠恕者,其心实异。……曾子之言,盖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学者默识于言意之表,则亦足以互相发明,而不害其为同也。”
其次,从诠释的角度来看,朱子对此章之诠释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以理学精神解释经典,体现出经典理学化的诠释特色。正如谢上蔡所言,对忠恕的理解难处并不在于训诂,而在于义理。近人程树德称,对此章义理理解主要存在两种意见,“此章之义,约之不外一贯即在忠恕之中及在忠恕之外二说。”①朱子从理学立场出发来解释忠恕一贯,认为忠恕即是一贯,忠为一为体,恕为贯为用,通过此章诠释阐发理学“理一分殊”这一重要思想。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尤其清代汉学家,多将忠恕看作行事,是“以尽心之功告曾子,非以传心之妙示曾子。”并批评《集注》“独借此大谈理学,”反映出与朱子不一样的诠释立场。
二是在继承前辈之说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理解,体现出精于择取而自出新意的特点。无疑,朱子对“忠恕一贯”的理解以二程思想为前提,但是我们应看到,朱子所选取的二程说是经过细致甄别选取的,剔除了其中认为不合适的部分,如他认为小程子引《孟子》“尽心知性”说、“忠恕贯道”说,《中庸》“君子之道四”说解释此章不可晓、有误。针对程门弟子各不相同的看法,他做出了精细的辨析取舍,特别是朱子采用《中庸》“至诚无息”诚本体说解释此章所蕴含的道之体用说,体现出他的创造性。
三是突出语境对文本的影响,讲究诠释的灵活性,以达到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的诠释目标。朱子有着明确强烈的诠释意识,认为诠释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将圣贤原义客观地挖掘呈现出来,以帮助学者加深理解。故此,他抓住“忠恕”在《论语》与《中庸》中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客观事实,指出二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指向,孔子之言与曾子之言深层原意各有不同,不可拘泥,亦不可牵合表层文字之同。学者应默识于言意之表,互相发明圣贤之意。
四是突出诠释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以达到针砭学弊,端正为学方向的诠释目标。划清儒学与佛老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纠正为学弊端,端正为学之方的诠释追求在这一章诠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子本章诠释,矛头指向空虚顿悟的禅学、舍本求末的浙东功利学,舍末求本的张、陆心学,要求学者树立本末兼顾,真积力久,由用达体的为学之方,提出尤其应在分殊上下工夫。
第四节 道统之两翼:《四书》与《太极图说》
宋儒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亲切体贴与创造诠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话语,朱子道统论是其中最具创见、意义深远的枢纽话语之一,亦是近来朱子学研究的热点话题。①本节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朱子道统世界究竟是如何构成的?朱子如何使道统思想的建构、《四书》新经典的诠释、理学思想的推崇三者相统一?如何看待周敦颐的道统地位?“太极”概念所代表的《太极图说》与《四书》在朱子道统世界中究竟居于何等地位?显然,朱子在一种注重文本诠释的看似保守的注述工作中,而寄托了极其新颖的理论创作活动,成功实现了中国经学范式从五经学向四书学的转移,并将宋学的精华——理学思想注入到了新经典体系中,从而既实现了经典再造,又做到了思想重构。用他的话讲,就是“刻意经学,推见实理”。朱子所成功开辟的这条经学再造与理学新思相统一的路线,真正实现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一致,挖掘其中的思想内涵,无疑对思考当下儒学经典诠释与思想创新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意义。
窃以为,朱子道统是由人物谱系、经典文本、核心范畴构成的精密系统,非止于《中庸章句序》“执中”之传。①它内蕴两条并行之路向:一可谓二程四书学工夫路线,其特点是认可二程传孟子之学,赋予《四书》以理学这一时代精神,突出格物等范畴的工夫教化意义。二可谓濂溪太极说路线,认可濂溪直传孟子之学。树立《太极图说》(含《通书》)为道学新经典,赋予太极范畴以形上本体意义。此“周程之学”体现了朱子道统中濂溪与二程、易学与四书学、本体与工夫的差异性和互通性,朱子有意强调了二者的独立性,其后学黄榦、程复心等则贯太极与四书为一,突出二者的一体性。朱子道统说正是通过对《四书》旧典的诠释与《太极图说》新典的推崇,树立了以周程道学精神为主导的道统谱系,形成了以《四书》和《太极图说》为主干的新经典范式,提出了一套涵盖工夫与本体的新话语系统,在继承之中实现了对儒学的更新和转化。
一 何谓朱子道统
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使用“道统”一词②,开篇即言:“《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③对“道统”与“道学”之定义及关系,学者有不同看法。陈荣捷先生区分了朱子道统的历史性与哲学性,强调了哲学性,肯定道统与道学的一体性。其《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言,“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性内在需要”。④余英时先生则从史家眼光出发,强调道统的外化和政治性,突出道统与道学、孔子与周公的差异性和断裂性:“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内圣外王无所不包……而孔子只能开创道学以保存与发明上古道统中的精义——道体,却无力全面继承周公的道统了”。①余氏突出道统与道学之辨,批评陈氏之说乃是采用后世黄榦之看法,混道统与道学为一。②且认为朱子道统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用意,据“《中庸序》推本尧舜传授来历”说,“完全证实了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是针对着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据比对《答陈同甫》与《中庸序》,认为“《中庸序》的道统论述是以该书为底本,已可以定谳”。③
余氏雄辩似有进一步讨论余地。首先,余氏对“道统”的考察可商。他认为朱子最早使用“道统”两字见于淳熙八年(1181)《书濂溪光风霁月亭》“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但“意指不很明确……大概此时他的‘道统’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④余氏之所以如此断定,是因为此处“道统”不合其心中“道统”必含政治之意,“道学”二字更合其意。其实,早在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榜文》中朱子已提及濂溪“心传道统”,即便在余氏认为朱子早已完全厘清道统与道学的绍熙癸丑(1193),朱子还是以“道统”称颂濂溪,《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言:“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可见,此道统并非一定含政治意义。朱子提及“道统”尚有以下五处,未见其必含政治义。己酉《答陆子静》“子贡虽未得承道统”⑤,丙辰《答曾景建》“况又圣贤道统正传”⑥,《语类》“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⑦,“则自汉唐以来,……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⑧,绍熙五年《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恭惟道统,远自羲轩”。①朱子《中庸章句序》认为孔子不仅不是所谓“道统的无力继承者”,反而是集大成者。颜、曾、思、孟传承光大道统,濂溪二程接续之,朱子本人亦“赖天之灵,幸无失坠”。《章句序》末言“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可见朱子隐然以传承道统自居。
其次,余氏认为朱子道统针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恰与朱子道统的“去政治化”用意背道而驰。《中庸章句序》所论道统的演变与《大学章句序》大体相同,朱子认为,孔子不得其位并没有妨碍其成就,他反因继往开来之贡献越过了尧舜,以学统的形式延续了道统,使借助学统形式所表现的道统依然保持了其独立性和超越性。朱子的道统与道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合②,孔子之后所传道学即道统之根本所在,即便是道统所涉帝王之治,亦当在道学范围内,如帝治当以格物正心为本。朱子坚持认为政治上的成就不能作为判定得道与否的标准。当弟子质疑“天地位万物育”仅指当权者时,朱子指出,反躬自修的穷乡僻壤之士亦能做到。③此与宋明儒学走向平民化、内在化的趋向一致,如过分突出道统的政治向度,则显然与此大趋势背道而驰。如余氏之解,则孔子以下已无“道统”可言。④
余氏为突出朱子道统的政治义,认为《中庸序》以乙巳(1185年)《答陈同甫》“来教累纸”书为底本的“定谳”恐难为“定谳”。然此书与《中庸章句序》仍有少许距离,而《戊申封事》及同时若干材料则几与《章句序》全同。⑤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子《中庸序》亦经反复修改而成,朱子癸巳(1173年)为好友石子重所写《中庸集解序》实为《章句序》之早期底本①。比较二序可知,其差别主要有二:其一,《集解序》仅从孔、曾、思、孟立论,未提及《章句序》尧舜禹汤等孔子之前道统谱系,此是一大变化。其二,《集解序》特意点明“濂溪周夫子”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道统枢纽地位,但《章句序》则只字未提。《集解序》还特意批评汉唐诸儒,尤其点出了李翱,此亦不见于《章句序》。
综上,笔者以为,陈荣捷先生从哲学角度判定朱子道统论更合乎实际。简言之,朱子道统指道之统绪,当含传道之人、传道之书、传道之法。其内容实由两条并列线索构成:第一个路向以二程为传人,以《四书》为载体,以工夫范畴为根本,其要乃在日用工夫。第二个路向以濂溪为传人,以《太极图说》为载体,以太极范畴为根本,其要乃在形上本体。
二 二程《四书》工夫道统论
(一)宗二程为统
朱子道统论具有树立道学正统,维护道学纯洁的目的。其道统谱系从立正统与判异学两面展开,立正统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一是尊孟退荀,二是摆落汉唐。三是宗主二程。需要说明的是,朱子虽对张载、邵雍、司马光之学亦有认可吸收,然亦不乏否定,较之二程,他们终是偏颇。朱子道统的“正统性与纯洁性”见诸其强烈的推崇洛学的学派意识,仅据《六先生画像赞》、《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并不能表明朱子认可张、邵、司马接续道统。此三种文字并未论及道统,且皆作于朱子道统思想尚未形成的癸巳前后。除《画像赞》外,余二者皆受吕祖谦很大影响,并非纯为朱子意。②四是排斥程门而自任道统。朱子不仅对汉唐诸儒未能传道不满,更明确表达了对二程之后百余年间道统传承的失望。尽管二程弟子众多,但朱子认为“多流入释氏”,未能接续二程之道,“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③当仁不让的认为自己虽私淑二程,却能接续其学。故《大学章句序》丝毫不提二程后学,直接自任接续二程之传。“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中庸章句序》直斥程门“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朱子道统论极其注重门户清理,即便理学内部,亦严加甄别,其“道学”所指含义甚窄。《宋史·道学传》于朱子同时学者,仅列南轩,而置陆九渊、吕祖谦于《儒林传》,实据朱学立场。
在树立正统的同时,排斥“异学”亦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使命所在。《学庸章句》二序皆特重判教,此判教当分三层:最要者是“弥近理而大乱真”的佛老之学,第二层则是与儒学有各种关联的流行之说,俗儒记诵词章之习,权谋术数功名之说,百家众技之流。凡非仁义之学,皆在批评之列。朱子一生与人发生多次学术辩论,即与此有关。第三层则是渗入儒学内部的不纯洁思想。朱子对此尤为关注,早年所撰《杂学辨》即批判吕本中、张九成等前辈学者溺于佛老,陷入异端。丁酉《四书或问》对程门诸子严加辨析。于同时代学者,尤为痛斥陆九渊之学流入佛老异端,实为“告子之学”。但朱子通过判教所树立的“道学”,当时即引起时人不满,陆九渊即对朱学树立门户、张大“道学”一名深表忧虑,言“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①道学之外的周必大亦对此严加批评。②
(二)推《四书》为经
朱子在继承二程表彰、阐发《四书》的基础上,首次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一有机整体而加以全面注释,最终使“四书学”取代“五经学”,成为宋末以来新的经典范式。朱子对《学》、《庸》、《论》、《孟》的特点有清晰把握,指出《大学》通论纲领,阐明为学次第,亲切易懂,确实可行,在四书系统中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首要意义。《论语》多为对日用工夫的即兴阐发,可树立为学根本,但文字松散,义理不一,故初学不易把握。《孟子》则注重对义理的发扬阐发,易于感动激发人心;《中庸》工夫细密、规模广大、义理深奥,多言形上之理,最为难懂,故作为《四书》的殿军。“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①朱子自认用功最多,成就最大者为《大学章句》一书:“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②他将《大学》视为《四书》枢纽,认为实质上起到对其他三书的贯穿作用。常以“间架”“行程历”“地盘”“田契”“食次册”等形象说法强调《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纲领地位,《论》、《孟》、《庸》可以说皆是《大学》的填补与展开,但从义理言,《四书》各书无有高下之分,他批评了《论语》不如《中庸》的观点。
就《四书》与五经的关系,朱子多次从工夫简易、义理亲切的角度肯定《四书》在为学次序上先于五经。当由《四书》把握为学次第规模、义理根源、体用纲领,再进而学习六经,方能有得。他以“禾饭”“阶梯”“隔一二三四重”的形象譬喻传达了二者在教法、效用上存在难易、远近、大小关系。“《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③“四子,六经之阶梯。”淳。④朱子以自身为学实践为例,甚至将经学所得比作“鸡肋”,以此告诫学者,不应重蹈其覆辙,而应直接就《四书》现成道理探究。朱子继承发展了程子“《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知而明”的思想。认为《四书》作为阐明义理之书,对其他著作的学习具有标尺意义。掌握了《四书》这个义理中心,就等于掌握了根本,由此理解其他一切著作,皆甚为容易。故他对《四书》穷尽毕生精力,每一用语皆费尽心力,称量轻重适中,方敢写出,生怕误解圣贤本意。连无关紧要的虚词,亦反复掂量,以达到丝毫不差的精细地步。
(三)以工夫传道统
朱子注释《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落实道统观念,以道学思想规定道统内容。《四书集注》始于道统、终于道统,《大学章句序》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道统,《孟子集注》终于明道接孟子千年不传之学。从道统传道人物来看,孔、曾、思、孟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传承四子思想的经典相对应。学界对朱子道统的认识通常局限于《中庸章句序》之十六字心传,此“执中”之传仅为《四书》道统之一部分,仅以精一执中之传无法限定、解释朱子广大精密的道统系统。我们将视野拓展至全部《四书集注》时,发现其中充满了朱子的道统观。《中庸章句》开篇序引程子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强调子思传孔子之道于孟子,其要在理事、一多范畴。《中庸》实以道之体用为中心,费隐章、诚明章作为管束全篇之枢纽性章节,皆阐明此意。《论语》亦多处论及道统之传。《论语集注》点出颜子、曾子对夫子之道的领悟与承当,“忠恕一贯”是“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是曾子传道工夫根本所在。“克己复礼”被称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体现了儒家道统之孔颜授受,朱子数次将之与精一之传相提并论。此外,朱子对“斯之未能信”“曾点气象”“逝者如斯夫”等章皆是从见道、体道角度阐发之,指出此皆关乎道之体认与传承。《论语集注》末“允执其中”章引杨时说,言《论语》、《孟子》皆是发明儒家道统之书,指出圣学所传,乃在中道。《大学章句序》以性气之别为理论基础,逐层阐明以复性之教为中心的儒学道统论,建构了由政教合一至政教分离的道统演变史,批判了道学之外佛老、词章、功名等诸说流弊,突出了二程及朱子传道地位。强调《大学》格物、诚意直接贯通道体,是能否传承道统的工夫要领。朱子将《孟子》列于《四书》,决定性地结束了孟子地位之争,确定了孟子道统地位。《孟子集注》称赞孟子仁义论、性善论、养气论皆是发前圣所未发之论。把尧舜性者章上升到传道高度,称赞明道对尧舜与汤文武性之、反之的二重判定极为有功,显示明道学达圣域,否则不足以言此。末章点明孟子依次序列群圣之统绪,表明先圣道统传承所在,将传诸后圣而永不坠落。
朱子尤重以工夫论《四书》,正如学者所论,朱熹的《四书》学“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①故对工夫范畴的阐明,既是朱子理学思想要领所在,亦是其道统论根基所在。在朱子看来,工夫实践是第一义的,无体道工夫,则不可能领悟道,更无法传承道统。《四书集注》创造性地诠释了《四书》系列工夫范畴,与道统最密切者有主敬、格物、诚意、慎独、忠恕、克己等。
朱子对十六字心传的阐发围绕存理灭欲的存养省察工夫展开。不仅尧舜禹汤孔子等以精一执中工夫传道,颜、曾、思、孟亦皆以各自入道工夫传承道统,无工夫则无法传道。其《答陈同甫》先阐发十六字心传精一工夫,紧接着指出夫子于颜、曾、思、孟之传亦是如此,四子分别以各自工夫传道,颜子以克己、曾子以忠恕、子思以戒惧、孟子以养气,鲜明体现了儒家工夫道统相传之妙。主敬是朱子的工夫要旨。朱子视敬为成就圣学必备工夫,始终深浅,致知躬行,无时无处不在,称赞敬为圣门第一义,为工夫纲领和要法,“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①多次从工夫道统的角度论敬,指出尧舜以“敬”相传,敬贯穿圣人所有言行,为其作圣根本。“圣人相传,只是一个字。……莫不本于敬。”②程子以敬接续道统。“至程先生又专一发明一个敬字。”③强调程子对敬的发明远迈前人,盖圣人只是论说“敬目”,而未曾聚焦于“敬”自身意义,程子将“敬”脱离具体语境,突出为独立的具有本体意义的修身工夫,“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④朱子认为可由敬而入道、传道,尽管颜回克己与仲弓敬恕工夫存在高下之分,但敬恕亦能达到无己可克的人道境界。
格物是朱子工夫论的核心概念,朱子从道统高度来认定格物的意义。言:“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曾说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无复遗虑。然程子既没,诸门人说得便差,都说从别处去,与致知、格物都不相干。”⑤朱子对韩愈道统地位排斥的一个重要根据,即是基于其对“格物”的忽视,格物是入道必经之门,无格物者,其所有工夫只是一“无头”工夫。在朱子看来,忽视格物工夫的学者没有资格纳入道统谱系,这极大强化了道统的道学属性。朱子推崇程子格物说,批评程门亲传弟子未能传承发挥其格物工夫,故未能接续道统,而自身则上接二程格物,故得承道统。朱子的格物之学乃围绕成就圣贤展开,只有为圣贤之学服务,格物才可能“是(朱子)他全部哲学的一个最终归宿。”①《四书集注》据格物以阐述孔、曾、思、孟圣贤境地,充分显示了格物贯穿全书的枢纽地位。朱子对“诚意”之重视与开拓,绝不亚于“格物”,提出“诚意”是“自修之首”,是衡量修养境界的根本标准,是人鬼、善恶、君子小人、凡圣的分界点,“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②。“诚意是善恶关。……诚意是转关处。……诚意是人鬼关!”③“知至、意诚是凡圣界分关隘。”④朱子释诚意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⑤此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一于善”,意有善恶之分,故需要诚之实之功夫来贞定意念的价值指向,使所发意念皆归于善。用“一”,强调了意念归于善的纯粹性、彻底性、连续性。“善”则指明了意念的性质。诚意之学于朱子学术、人生、政治皆具有某种全体意义。它不仅是朱子诠释的对象,更是一生道德修养之追求。朱子以“格君心之非”为治国之纲领,将“诚意毋自欺”视为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根本,多次向帝王上书强调诚意正心之学的重要。第二层是诚意蕴含慎独,《大学》、《中庸》皆言及慎独工夫,慎独是谨慎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而审其几。《中庸章句》指出慎独是在心之未发已发之际的工夫,在隐秘幽暗的状态下,审视事物之几,以遏制人欲于萌芽状态。能否实现诚意,做到中道,皆取决于慎独。如上两节所述,关于颜子“克复心法”、曾子忠恕之传,皆是突出了二子修身工夫之重要,故可视为“十六字心传”之重要补充。
三 濂溪《太极图说》形上道统论
(一)以濂溪为统
濂溪在朱子道统中的地位,是一让人颇感困惑的老问题。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道统论最要者在此,最困难者亦在此,《新道统》言:“乃孟子与二程之间,加上周子,此为道统传授最重要之改变。”①“朱子此一抉择,至为艰难”。②最争议者依然在此,“此为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争论未已”。“所谓两程受其学于周子,殊难自圆其说”。③认为朱子将濂溪列入道统纯粹出于哲学(处理理气关系)而非历史原因。然朱子对濂溪的态度亦令人无所适从④:一方面,朱子明确二程直接孟子之传,如阐发道统说最要的《学庸章句序》丝毫未提及周敦颐,但癸巳《中庸集解序》曾明确濂溪上接孟子而下传二程,“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如何至于后来,反而删除之?或许,如于《四书》中确认濂溪上接孟子,则很难在《四书》系统内解释濂溪对孟子的继承和对二程的开启,亦将与二程不由濂溪而上接孟子的说法相冲突,盖在二程道统谱系中其实并无濂溪位置。程颐为明道所作《墓表》言:“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明确宣称自悟“天理”而非“太极”本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⑤此或《四书》道统添入濂溪困难所在,故朱子干脆删除之。⑥朱子将濂溪从《四书》工夫道统剔除并不意味着置濂溪于道统之外,其他相关文字反复推尊濂溪得孔孟道统之传而开启二程,具有如夫子般“继往开来”之地位。在淳熙四年至十年所撰五处濂溪祠堂记中,朱子皆阐明濂溪的传道枢纽地位。如淳熙四年《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言:“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①五年《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言:“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河南两程先生既亲见之而得其传。”②六年《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则将濂溪太极说与《四书》联系起来,认为太极之说实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在传承,完全合乎圣人之言,以称颂孔子的“继往开来”来称赞濂溪,视其为旧儒学之接续,新儒学之开创者,在道统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③八年《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则进一步将濂溪太极之学与《四书》工夫道统相贯通。指出濂溪学主旨是格物穷理,克己复礼,实与《四书》内在一体。“诸君独不观诸濂溪之图与其书乎!……然其大指,则不过语诸学者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④十年《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更进一步,从明天理、传道学的角度称颂濂溪,概述其阐明天理本体、揭示克复作圣之功的本体与工夫两面贡献,孟子以下,一人而已,开创儒学复兴新局面之功无人可比,评价无比之高。“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盖自孟氏既没,而历选诸儒授受之次,以论其兴复开创,汛扫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⑤可以看出,朱子数篇祠记对濂溪的评价,时间愈后,评价愈高,定位于继孔孟而开二程,并有意将其太极本体理论与四书工夫理论相关联。
与《四书》道统不提甚至撇开周程关系不同,朱子晚年两篇文字中特别提出“周程”说,强化二者授受传承关系。绍熙癸丑(1193)《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直接提出周程接续孟子之道,“自孟氏以至于周程”。⑥绍熙五年(1194)《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强调周、程“万理一原”的道统传承,祭祀圣贤的释菜之礼,亦以濂溪、明道配。“周程授受,万理一原。”但朱子强化周程授受关系的看法曾遭到好友南轩、汪应辰等质疑。他们认可二程早年受学于濂溪这一事实,但并不认同二程传濂溪之道,最根本的是二程不认可这一点,且对濂溪似有不敬。①二程与濂溪的理论路线、经典取向并不一致,二程更重视《四书》的工夫教化论,由工夫而领悟天理本体。即便伊川重视《易》,其路向亦与濂溪亦迥然不同。为此,朱子坚持论证濂溪传道二程,认为当从不受重视的《通书》入手,方可看出二程得濂溪之传而广大之。朱子提出二程阴阳之说、性命之论等皆受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影响,根据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定性书》、《李仲通铭》、《程邵公志》,此种《铭》、《志》论述实不足为据。至于《好学论》、《定性书》是否在精神实质上与濂溪一致,亦可商讨。朱子己丑(1169)《太极图说》建安本序认为,二程性命之说来自《太极图》、《通书》,具体证据是《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与二程的一《志》、一《铭》、一《论》关联密切。己亥(1179)南康本《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主张二程论述乃是继濂溪《太极图说》、《通书》之意,一《志》、一《铭》、一《论》尤其明显,不仅师其意,且采其辞,更外在化。有学者认为二程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②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二程因受学于濂溪而得孔孟之传,且传其《太极图说》、《通书》,突出了周程授受对于二程道统地位确立具有决定性地位。可谓无濂溪之传,则二程不可能得传道统。二程之外,亦无人能窥濂溪之意,故二程没而其传鲜。此既突出了濂溪悟道之高,又点出周程授受之唯一性。朱子解答南轩二程未道及《太极图》的原因是“未有能受之者”,骤然传之,反致不良影响。
朱子以濂溪《太极图说》为主的道统论①,在人物谱系上突出了伏羲和濂溪,在经典文本上以《太极图说》为中心,在范畴诠释上彰显了“太极”的形上意义,为朱子理学本体论建构奠定了根基。朱子以“同条而共贯”说阐明以太极为中心的道统论,指出伏羲易始于一画、文王易开端于乾元,太极概念始于夫子,无极、《太极图》则濂溪言之。四说虽异,其实则同,关键在实见太极真体。《答陆子静》言“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②朱子比较了伏羲与濂溪之学,判定濂溪太极图是自作。以阐发易学大纲领,义理精约超过了先天图,但规模不如其弘大详尽,故仍处先天范围内,而无先天图之自然纯朴。《答黄直卿》言:“太极却是濂溪自作,发明《易》中大概纲领意思而已。故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之精而约。”③
(二)《太极图说》的本体论
朱子哲学体系主要通过诠释濂溪《太极图说》形成。前辈学者冯友兰、钱穆、陈荣捷等早已指出朱子哲学与《太极图说》的密切关系。陈来先生指出,“朱熹以太极为理,利用《太极图说》构造理学的本体——人性——修养体系,这是理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④以下讨论朱子对太极、诚、圣人三个相应概念的阐释。朱子是理太极的代表,把太极解释为理,视为理之极致,“(太极)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⑤又认为太极只是指示万善总会的表德词。“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⑥太极还是生生无穷之理,是万物产生之本根,“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太极图解义》认为太极作为阴阳动静根源之本体,并不脱离阴阳而孤立,是即阴阳而在之本体,突出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朱子分析了太极本体与分殊之理的关系。《太极图说解》的“统体太极”和“各具太极”阐明了作为万理之源的太极与无数分理的关系。自男女、万物分而观之,各具一太极,全体合观,则是统体太极。此两种太极在理上并无不同。朱子人性论以太极阴阳的理气同异说为理论基础。人物禀太极之理而为性,禀阴阳之气为形,此理气凝聚构成人之性形。人物性同气异的原因在于:人物皆具同一太极之理,在气化过程中,只有人禀赋阴阳五行之灵秀,故人心最灵妙而能保有性之全。在人性论上,朱子主张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所谓气质之性,乃是作为太极全体的性落入气质之中,它并非天命之性的另外一种,而是天命之性的一种现实形态。朱子追溯此论之源头,认为孔孟虽内含此说,然程、张因濂溪方才发明此说,程子性气之论来自濂溪,若无濂溪太极阴阳说,程子无法提出此说。“此论盖自濂溪太极言阴阳五行有不齐处二程因其说推出气质之性来,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①总之,朱子对濂溪《太极图说》太极本体论思想的挖掘,构成其道统论的本体面向。
立人极之圣人。《太极图说》下半部分论述了太极的人格化——圣人,是太极思想在人道领域的落实。②圣人是太极的人格化,全体太极之道而无所亏,保全天命之性而无所失,定其性而不受气禀物欲影响,故能树立为人之标准。朱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全体太极”以定性,以立人极。圣人在德性上具有如太极般的全体性(全具五常之德)、极至性(中正仁义之极)、自然性(不假修为)。“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通书》对圣人特点发明详尽透彻。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实理性、太极的浑然全体性。“孔子其太极乎!”通变无碍性,“无不通,圣也。”“大而化之”的“化”性。“圣者,大而化之之称”。朱子《四书》对“人极”亦有论述,《学庸章句序》皆以“继天立极”开篇,其“立极”当指“立人极”。“继天立极”指圣人继承天道以挺立人道,此立人极者亦即尽性者,故天命为君师教化民众以复其性。《四书集注》亦多次以“太极”解释夫子之圣,圣人是天理、天道之化身,如太极一体浑然而备阴阳正气,动静行止,皆如太极动静之显发。其外在容貌间所呈中和气象,显与天合一之境界。“子温而厉”章注:“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
“诚,即太极,圣人之本。”诚被朱子视为与太极、圣人对应的本体概念,诚是“实理”。圣之为圣的根据就在于诚。诚具有太极、圣所共同具备的特点:全体、内在、超越、自然、通化等。《通书》乃发明《太极图》的表里之作,首章“诚”完全对应于《太极图》,朱子《通书注》说,“诚即所谓太极也”。诚之源为“图之阳动”;诚斯立为“图之阴静”;诚之通、复为“图之五行之性。”诚是圣人的独特属性,只有圣人能保全此诚。“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诚的本来意义是真实无妄,其形上意义则是天命之性(理),是事物内在禀有之理。朱子强调了诚的实理性,万物资始是“实理流出”,各正性命是“实理为物之主”,纯粹至善是“实理之本然”。认为《通书》“诚神几曰圣人”的诚、神、几分别指实理之体、实理之用、实理之发见。指出诚具有自然、简易的特点。“诚则众理自然”。但诚与太极、圣人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它还有工夫意义,是贯通天道与人道的连接者。朱子明确区分了诚的这两层意义:《中庸》的至诚指“实有此理”,诚意则是工夫之诚,不欺之诚。汉唐学者皆以忠信笃实之德言诚,朱子称赞二程以实理言诚实为创见,并提醒要兼顾诚的这两层含义。“诚,实理也,亦诚悫也。由汉以来,专以诚悫言诚。至程子乃以实理言。”①
(三)推《太极图说》为经
朱子通过精心诠释和大力推崇,将《太极图说》树立为道学首要经典,指出《太极图说》是言道体之书,穷究天理根源、万物终始,自然而成,并非有意为之。《与汪尚书》言:“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①认为该书对工夫问题论述甚少,仅限于修吉、主静,朱子则将主静转化为主敬,他高度评价《太极图说》、《通书》,认为所论如秤上称过,轻重合宜而精密无差。“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轻重极是合宜。”②视《太极图》、《西铭》为孟子之后儒家最好著作,甚至认为《通书》比《语》、《孟》尚且语义分明,精密深刻,布局严谨。“《通书》比《语》《孟》较分晓精深,结构得密。”③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濂溪之书远超秦汉以下诸儒,条理精密、意味深刻,非潜心用力,不能明其要领。认为《太极图》具有首尾相连、脉络贯通的特点,《图说》上半部五段对应五图阐发了太极阴阳生化过程;下半部分论人所禀赋的太极阴阳之道,与上半部相应,体现了天道人道一体的观念。首句一一对应上半部分,人之秀灵即是太极,人之形神则是阴阳动静,五性则是五行,“善恶分”则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事出”为万物化生。自此而下的“圣人定之”句,体现圣人得太极全体,而与天地混融为一,实现了天人相合。故《太极图说》与《中庸》皆阐明天人合一、贯通形而上下这一主题。
朱子强调《通书》围绕太极这一核心概念来发明《太极图》之蕴,透过《通书》方能清楚把握《太极图》的主旨,若无《通书》,则太极图实不可懂。“《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④《通书后记》指出《通书》和《太极图说》是表里关系,是对《太极图说》太极阴阳五行的阐发,实为道体精微之纲领,并强调了义利文道之取舍,以圣人之学激发学人走出功名富贵文辞卑陋之俗学,对为学工夫、治国之方皆有亲切简要、切实可行的阐述。朱子早在己丑《太极通书后序》就指出《太极图》是濂溪之学妙处所在,《通书》用以阐发《太极图》之精蕴。淳熙己亥《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指出《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尤其阐发《太极图》之奥妙。还以“诚无为”章具体论证与太极阴阳五行说的对应。《近思录》开篇所选周子说,亦是《太极图说》与本章,可见朱子对此章之重视。①朱子对《太极解义》极其满意,认为恰到好处地阐发了濂溪之意,达到了“一字不可易处。”②朱子可谓对濂溪《太极图》用力最深,最有创见者,采用章句分解形式,以注经的严谨态度疏解此书,最终使得该书层次分明,粲然可读。经由朱子的大力推崇,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太极图说》道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四 工夫与本体:《四书》与《太极图说》的贯通
(一)《太极图说》与《四书》的贯通
朱子广大的道统体系由《四书》和《太极图说》所代表的工夫、本体双主线构成,二者相互贯通,体用一源,工夫是通向本体之理的手段,本体是分殊工夫的最终实现,工夫不离本体指引、范导,本体端赖工夫真积力久,可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朱子阐明了《四书》与《太极图说》的密切关联。《四书》虽以日用工夫为主,然工夫以太极本体为理论基础,指向道体之领悟。如朱子的格物穷理就是通过不断穷究事理,积累贯通,达到豁然开悟,物理明澈,心与理一的心体光明状态。《大学或问》以《太极图说》无极二五的理气说解释人物之性形。天道流行发育,以阴阳五行作为造化之动力,而阴阳五行的出现又在天道之后,盖先有理而后有气,故得理为健顺五常之性,得气为五脏百骸之身。《中庸章句》多言形上之道,其性、体用、诚论,皆与《太极图说》息息相通,不离理气先后、理气离杂、理一分殊、理气同异、天人一体等命题。如首章指出性专言理,道兼言气,在道的意义上是理在气中而理气不杂,正如太极阴阳之不离不杂。采用太极阴阳五行解释健顺与五常,性即太极,健、顺分指阳、阴,仁义礼智对应五行,将人性健顺五常与太极阴阳五行严密对应,体现了天人的一体性。以理一分殊、理同气异解释《中庸》性、命之说。凡涉及人物之性,皆以性同气异、理一分殊解之。从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释“不诚无物”,强调理在物先,理内在包含了物。朱子同样以理一分殊、理同气异释《论孟》重要章节。如提出忠、恕分指理一分殊、体用、天道人道,忠是理一,恕是分殊,忠为恕体,恕为忠用,忠指天道流行,恕则各正性命。以理一分殊说阐发见牛未见羊章、君子之于物章所体现的儒家之爱的差等性与普遍性,以理气先后阐发浩然之气章、性命章、异于禽兽章、生之谓性章等,特别提出儒家人性思想直到周子太极阴阳五行说出,方能阐明性同气异,程、张人性论皆是受濂溪阴阳五行说影响,突出了濂溪的开启之功。“及周子出,始复推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则同,而气质之所从来,其变化错揉有如此之不齐者。……此其有功于圣门而惠于后学也厚矣。”①“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②尽心知性章引张载说,并将之与《太极图》相对应,太虚即《太极图》最上圆圈无极而太极,气化之道即阴阳动静。
(二)朱子后学绾合《太极图说》与《四书》
朱子后学基于朱子对《太极图说》与《四书》内在关系的阐发,进一步绾合二者,树立了《太极图说》与《四书》为源与流、本体与工夫关系的认识。黄榦是阐发朱子道统论最有力者,对此亦多有阐发。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指出:
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赋于人者秀而灵。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物之生也,虽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人中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尧之命舜,则曰“允执厥中”中者……则合乎太极矣。③此以《太极图说》的太极阴阳五行论儒学道统,太极二五理气之合而生人物,人得其精气而秀灵,虽物之偏塞亦皆不离太极。圣人则是人中最秀灵者,故能继承天道以确立人极,而获道统之传。此一论述完全将儒学道统置于太极本体的天道基础上,与《尚书》“十六字心传”置于圣人之传不同,突出了道乃是合乎太极本体,因应万物生成而来。勉斋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周、程、朱子道统之传,多以《四书》一二核心工夫词概括之,且皆与太极相合,体现了勉斋以工夫为重的道统特色。显然,勉斋所建构的工夫道统,确有其“武断”,然此“武断”把握了道学重视下学上达的道统特色。勉斋另一鸿文《朱先生行状》则有意区别了朱子的为学与为道,指出其为道是以太极阴阳五行论天命性心五常之德:“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①可见勉斋始终置太极之学于道统之首,此亦正合乎陈荣捷先生以补入太极为朱子道统观念最具哲学性之改变的看法。
元代朱子后学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亦将《太极图说》与《四书》,太极与道统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结合。他在全书开篇处即采用十节图文依次论述从伏羲到朱子的传道系统,尤以《太极图说》为中心,突出了周敦颐与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指出程子去世后,周程所接续的以太极为核心的儒家道统面临中断危险,幸得朱子重新对周程易学作了深入阐发,学者如能反求诸心,以主敬为工夫,则能体悟太极内在于人,实为心之妙用,故以太极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实皆本诸于心。“又幸有朱夫子以发其精蕴,学者苟能求之于心,主之以敬,则知夫太极者,此心之妙用;《通书》者,又太极之妙用。”此把主敬工夫与太极本体相贯通。复心通过横渠、朱子说以证明二程在太极阴阳这一传道核心上与濂溪所接续伏羲之传一致,并以此作为列《太极图说》于《四书章图纂释》之首的原因。特别表明本书将《太极图说》置于编首的意图,意在显示周子《太极图说》端为《四书》道统之传、性命道德之学的本原所在。“故特举先生《太极图说》于编首,以见夫《四书》传授之奥,性命道德之原,无一不本于此《太极图说》”。既然周子是通过对作为《四书》源头的“太极”的图说来阐发、接续儒学之道,那么对作为“太极”之实质传承的《四书》自然亦可以“图说”了,此即其图解四书,“立图本始”所在。
在《太极图说》《四书》与朱子道统关系上,我们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夸大《太极图说》代表的道统对于《四书》道统的“纲领性”和“含摄性”。如有观点认为,“朱熹本于易道,起自伏羲的道统可以含摄本于《尚书》起自尧舜的道统”。①其实《太极图说》与《四书》道统分别侧重道统本体向度和工夫向度,二者可谓源流关系,理一分殊关系,不可偏废。如就朱子终生奉为圭臬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之教而言,他当更重视下学一面的《四书》道统。盖朱子哲学“非以本体论宇宙论为归宿,而重点在乎人生,即在乎《四书》之教。”②二是日本学者山井涌教授因《四书集注》未见“太极”而提出太极于朱子哲学并非重要的结论,陈荣捷先生作《太极果非重要乎》驳之,认为“太极乃本体论与宇宙论之观念,而《四书》则勿论上学下学,皆针对人生而言。”③其实,太极概念未见《四书集注》极为正常,此符合朱子不以难解易、不牵扯它书的解释原则。如朱子批评南轩《孟子解》的重大失误在于以太极解性,“盖其间有大段害事者:如论性善处,却着一片说入太极来,此类颇多。”④太极在朱子看来,其实为理,故朱子虽论太极不多,然处处论理,善观者当就朱子论理处观其太极说,而非必紧盯是否出现“太极”之名。盖一则太极经朱子之诠释、辩论而得以形成理学之最高概念,它本不如理、仁等概念易知;二则太极为形上抽象概念,属于儒者罕言的“性与天道”之范畴,朱子虽以太极为其哲学基石,然其教之重心,仍在《四书》的分殊工夫一面。故由朱子罕言“太极”之名不等于朱子罕言“太极”之实,亦不等同太极于朱子并不重要。
总之,朱子不仅使道统成为一个新范畴,而且使之成为一个工夫与本体兼具、天道人道并贯的广大精密系统,它含摄了朱子理学形上建构和形下实践的核心范畴。朱子的道统世界实现了思想建构与经典诠释、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一方面,他以极具时代感的道学精神诠释《四书》原典,使先秦《四书》与作为时代精神的道学融为一体,随着《四书》成为新的经典范式,道学亦实现了其经典化,成为儒学新发展之主干。另一方面,他极力推尊周程,精心诠释道学著作,使《太极图说》成为足与《四书》相当的道学必读经典,构成了以《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为主的道学新经典,道学文本的经典化极大树立了道学的权威地位,强化了道统的道学特色。朱子的思想建构依托于对道学范畴的创造性诠释,他的道统世界奠基于对道统、太极、格物等系列范畴的开创性诠释上,这些范畴与其经典诠释浑然一体,影响了身后数百年儒学的发展,是贯穿后朱子时代理学发展的主线,直至今日仍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转化不可或缺的资源。
第五节 道统的“门户清理”
在朱子漫长的为学历程中,从学李延平是个极重要阶段,它促使朱子断绝了对佛学的留恋,走上了以“四书学”为学术重心的圣学之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其重要标志是朱子于延平去世后不久即撰成清理儒学内部阳儒阴佛思潮的《杂学辨》,该书尤以对张九成《中庸解》的批判为中心。朱子的辨张无垢《中庸解》实为其早年思想的一次重要总结,在其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不可忽视的意义。故本节以《杂学辨》中辨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阐释朱子对《中庸》性道、戒惧、忠恕、诚、知行诸核心概念的认识,揭示其此时的中庸学水平,阐发其辟佛老、重章句的学术风格。参照晚年对《中庸》之论述,可以清晰地揭示朱子早年中庸学的得失、因袭、修正之处;这同时又是朱子在完成自我修正后对洛学门户的一次大清理,集中展现了朱子的佛教认知,显示了朱子的强烈卫道意识。故探讨该书,可以充实丰富朱子早年学术思想研究,对把握朱子思想的演变、朱子的道统意识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朱子辨无垢《中庸解》乃是接着从学延平而展开的,故先略述延平对朱子中庸学的影响,然后展开朱子对无垢《中庸解》批评的论述。论述以相关概念为主,重点在三个方面:朱子此时中庸学水平与晚年的异同比较;朱子此时对佛学的认知态度;朱子的解经方法始终表现出对章句之学的重视。透过历时演变的眼光看待朱子思想的因袭变化,阐明其道统思想的辟异端之面向。
一 “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朱子在从学延平之前就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受到正统有序的理学教育,他曾说自己十六岁就知理学是好东西。因家学和师长的熏陶,自小熟读《中庸》。与此同时,亦接触到禅学,并一度对之迷恋,早年诗作《牧斋净稿》即是明证。故当他二十四岁拜师延平后,延平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以所传“龟山指诀”,将其引导到理学正轨上来,分辨儒佛之异。延平为龟山高弟罗从彦之徒,得道南一脉之传,为学特重《中庸》,称赞该书将儒家成圣之学的工夫路径显示得清楚详尽,毫无遗漏。《延平行状》说:“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①延平思想最大特色在于从未发已发入手,通过静坐涵养的工夫,来体认未发之本体,由此达到切实自得、气象洒落之境界。“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②故其对朱子之教育,反复谆谆于“涵养”“体认”,惜乎朱子对此“龟山指诀”实不相契,转而喜从逻辑分析、章句考论入手,故二人于《中庸》章句之学讨论甚多。朱子此前因学禅之故,对本体思想有所了解。李侗为扭转其好佛趋向,授以儒学理一分殊之学,特别揭示分殊的重要,使朱子获知儒学体用不二、超越内在之精义,此点对其弃佛归儒影响甚大。概言之,此时朱子的中庸学具有以下特点:
在工夫进路上,特别注重道问学的一面,坚持认为道问学有其独立价值,是为道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夫(这一点与今人重逻辑分析之学相似)。朱子中庸学的一大特色就是自始至终注重章句文本之学。延平则认为为道“非言说所及也”,告诫朱熹“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而朱熹则“窃好章句训诂之习”,认为不展开谈说论辩,则于道理看不分明,于工夫偏颇不全。故晚年尚从为学博约并进的角度,当弟子面公开批评延平之学缺乏辨名析理的问学工夫。“然李终是短于辩论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①然而延平对涵养践履的强调,对朱熹形成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为学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本体论上,朱熹接受延平理一分殊之教,将之与对《中庸》中和的理解结合之。朱熹对延平“分殊”之教,尤有深刻感受,曾反思在见延平前自身为学染有一般学者通病:喜好笼统、高远、宏大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②而延平则教以“所难者分殊耳”。正是延平“所难之分殊”改变了他的为学方向,并成为他一生评判学术的标准。
此时朱熹自觉运用理一分殊之学来理解中庸(仁)。在对《中庸》性论的理解中,将理一分殊与未发之说结合起来。他说,“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窃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未发时看”。(先生抹出批云:“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③朱子认为,在理(性)一的意义上,生物皆同,在气禀(分殊)的意义上,人物有别。“理一分殊”表述的是理的本然状态,当从五常之性、本体未发时看待。延平则主张不能仅从未发、性内的割裂观点来看,当兼顾已发、外在,从全体连续的视角展开。朱子此时习于将仁与未发比配,如他认为“肫肫其仁”反映出全体是仁的义理,只有尽性之圣人方能做到。“全体是未发底道理,惟圣人尽性能”。延平则认为此是讲工夫所达的境界,不是谈义理。“乃是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④朱子对鬼神章的解释,亦是从“理一”这个本原兼含已发未发来看,“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窃谓此章正是发明显微无间,只是一理处”。⑤
延平对中和的解释亦是将理一分殊(体用)与中和未发已发相结合。他认为,从道的角度言,中和分指其体用;就人而言,则指未发已发。意味着道之体用与人之未发已发皆可以中和贯通起来,天人关系在中和那里得到协调统一。朱子称赞延平对此问题论述最详尽,当从体用来理解中和。“盖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则未发已发之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①朱子列举了延平几个重要说法。一是延平从《中庸》全书出发,确认未发之中是全书“指要”,可见未发之中的重要。“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②此较朱子《章句》所取龟山的首章为“一篇之体要”说更进一步。二是如何才是未发。延平说,“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③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人内心都会有无喜怒哀乐情感的时候,但这一无所喜怒哀乐之时并不等于未发之中,判定未发的标准不是外在情绪的宁静或波动,而是内心是否有主宰。未发之中实质是道德修养状态上升到相当高度才有的精神状态。外在情绪的发出与否只是一种表象,不能把表象当作实质。这一解释符合程门学派的精神,与朱子晚年对中和的理解一致。三是对“中和”具体字义、次序的理解。如延平把“致中和”的“致”解释为动态意义的努力、实现,符合《章句》“推而极之”的理解。在工夫次序上,延平明确提出中和境界必先经由慎独工夫方能实现。“又云致字如致师之致。又如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④须指出的是,以上对延平的反思回忆之说,符合朱子自身后来见解,但朱子明言当时并无此等领悟。此时他的看法是,认未发、大本为理一,已发、达用是分殊。延平纠正他将理一分殊与未发之说过于掺合的理解。如“太极动而生阳”朱子视为喜怒哀乐之已发,延平教导他这不是讲喜怒哀乐之发,而是阐发天人一理之同和人物分殊之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⑤
延平对朱子的影响还在于共同探讨二程、苏氏、吕大临、杨时等对《中庸》的解释,指导朱子收集诸家解说,扩大、加深对《中庸》的认识。作为道南学派的传人,延平师徒对杨时《中庸解》探讨最多。朱子后来在给林择之信中特别回忆龟山的中和说:“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①龟山的观点是未发体验中,已发获得和,以未发体验为工夫根本。朱子与此说不契,《中和旧说序》于此有深切追溯,“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②随延平探究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之说尚未领悟而先生已没,正是这种“未达”,促使朱子不断地进行探究。
四是延平非常注意纠正朱子的佛学倾向。如他批评朱子以“竿木随身”说解释《论语》“公山”章不合圣人气象,“竿木随身之说,气象不好,圣人定不如是。”③批评朱子对《中庸》“肫肫其仁”的解释,偏向佛学顿悟说,值得警惕。“大率论文字切在深潜缜密,然后蹊径不差。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恐其失处正坐此。不可不辨。”④批评朱子以孟子“必有事焉”一句解释“理一分殊”,有工夫落空陷入佛学之弊。“孟子之说,若以微言,恐下工夫处落空,如释氏然。”⑤针对朱子愧恨不能去心之弊,告之不可走向另一极端,“绝念不睬,以是为息念。”反复从“气象”上指出言辞有病,如“若常以不居其圣横在肚里,则非所以言圣人矣”“前后际断,使言语不著处不知不觉地流出来”等。延平对朱子的禅学底子有清醒认识,并不认为接触过佛学是坏事,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区分儒佛之异。他在《与罗博文》的信中说,“渠初从谦开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⑥
二儒佛之辨:辨张无垢《中庸解》
延平逝世后,朱子继续对《中庸》展开艰难探索,一个阶段总结性成果是在丙戌(1166年)冬撰写的《杂学辨》,该书分别批驳了《苏氏易学解》、《苏黄门老子解》、《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其中尤以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其实质是思想战线的一次交锋,通过划清儒与释老的界线,端正士子为学方向。故朱子特意挑选了在士子之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贵显名誉之士”,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士子会因崇拜名人而迷恋名人所崇拜的异端之学。“未论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选择张九成等名人加以批评体现了朱子的策略和勇气。朱子始终认为张九成佛学印迹特深,危害最大,“张公以佛语释儒书,其迹尤著。”九成与朱子所处时代最相近,对当时士子的影响最直接广泛;在学术渊源上与朱子又具有“血缘关系”,同出于龟山门下,与谢良佐亦有关联;且开启了此后朱子最大对手陆象山之学。对于这样一位“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释”的代表人物,朱子当然视为清理门户的首选了。朱子对无垢的著作有个基本判定,即“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效用之危害则是,“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故朱子毫不犹豫地亮出清理门户的卫道身份,以拯救世道人心,“尝欲为之论辨,以晓当世之惑”。朱子对张九成以禅解儒说的广为甚行极其担心,将其学说之流行喻为洪水猛兽。①无垢著作甚多,其佞佛最深者,则为《中庸解》,故朱子挑出全书五十二条予以批驳,“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②主要围绕性论、戒惧、忠恕、诚论、知行诸核心问题展开论辨,体现了朱子的佛学水平,反映出朱子此时中庸学的不成熟之处,显示出其对章句之学与辟佛老的一贯坚持,可谓早年学术之总结。
(一)性论:赞性、率性、觉性、见性
朱子对张氏性论的批评,针对其赞性、率性、觉性、见性说展开,体现了朱子此时对性的认识。“赞性”“体之为己物”。张氏认为天命之性说并没有对性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不过是称赞“性”之可贵,因其来源于天,是一普遍公共之状态,并未为人所个别拥有而“收为己物”。在率性之道时方才体性为自身之物,进入于五常之内。修道之教则表现为仁行于父子之类。“天命之谓性,第赞性之可贵耳,未见人收之为己物也。率性之谓道,则人体之为己物,而入于仁义礼智中矣……修道之谓教,则仁行于父子。”①朱子认为天命之性正是道出性之所以为性的本质所在,表明性是天赋人受,是义理之本原,非称赞性之可贵。并引董仲舒命为天令,性为生质说为证。反驳性“未为己物”说,既谓之“性”,则已经为人所禀赋了,否则无性可言。再则,性亦不存在待人“收为己物”。故张氏此说犯有两误。一方面人之生即同时禀赋天命之性,性与人俱生,否则人不成其为人矣。另一方面,性并非实存有形有方位之物,可收放储存,故以物言性不妥。“体之为己物”说亦不妥。性的内容乃是天赋之仁义礼智,并不需要待人去体验之,然后才入于五常之中。此皆不知为学大本妄加穿凿之病。再则仁行于父子等乃是率性之道而非修道之教,张氏颠倒道、教次序而不知。朱子晚年《章句》则从“理”立论,提出“性即理”说,强调性的普遍公共性,与此仅从人性上理解性不同。
“率性学者事,修教圣人功”。针对道、教关系,张氏作出两层区分:一是指圣人与学者的不同层次:率性是学者之事,以戒惧为工夫,修教则是圣人功用。修教之所以是圣人功用,是学者经由戒惧工夫而深入性之本原,达到天命在我境界后才能够发生的,以推行五常之教为主的效用。“方率性时,戒慎恐惧,此学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谓天命在我,然后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教,以幸于天下。”②朱子认为,率性之谓道是阐释道之为道的根据,意为遵循性之本然即是道,并非学者之事,亦不涉及戒惧之说。而修道为教是通贯上下的,贯穿了制定施为者圣人和修习者贤人。批评张氏直到深入性本原之说方才推行教的说法不合事理,将会导致遗弃伦理教化的后果,偏离儒家主旨,陷于释氏之说。“则是圣人未至此地之时,未有人伦之教……凡此皆烂漫无根之言,乃释氏之绪余,非吾儒之本指也。”二是指“离位”与否。朱子认为,率性并未离开性之本位,修道之教不可以“离位”来论,性不可以本位言,否则如物体一般有方位处所,“言性有本位,则性有方所矣”,与圣贤对性的超越说法相违背。再则无垢上章以“率性”为求中工夫,就“求”而言,则有离位之义。若非离位,何来求?
无垢认为,颜子由戒惧工夫,于喜怒哀乐之中悟未发已发之几,一旦获得天命之性善者,即深入其中,而忘掉人欲,丧失我心,达到一种无我无人,无欲无识的境界。“颜子戒慎恐惧,超然悟未发已发之几于喜怒哀乐处,一得天命之性所谓善者,则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丧。”还进一步提出,颜子拳拳服膺,实际已达到与天理为一,毫无私欲,人我皆忘的境地。所谓圣人,不过知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处,故当于此处求之。朱子指出《中庸》此处并无悟意,喜怒哀乐本即是性,中节即善,不存在得性与深入其善之说。否则,在此未悟之前,未得性而在性外乎?所谓“我心皆丧”说大大有害于理。张氏的“得性”说实际并非得到义,乃是领悟义。朱子为批评无垢,居然将“喜怒哀乐”之情直接等同于性,是非常罕见的(仅此一次)。尽管性由情显,但朱子成熟说法是喜怒哀乐是情,未发才是性,情有中节不中节之分,故不能直接说喜怒哀乐是性。
针对“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张氏提出人就是性,以人治人就是以我性觉彼性。“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觉彼之性。”①朱子指出,此非经文本意,乃释氏说。张氏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天命谓性,性无彼此之分,为天下公共之理,其理一也。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为人天生所固有,不存在得失假借之可能,故无法“以”之。张氏将见性与由乎中庸结合论述。“使其由此见性,则自然由乎中庸,而向来无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扫不见迹矣。”认为如有人能因他人之觉悟而见其本性,则自然能够实现中庸。而此前言行之无物无常,皆扫除无遗了无痕迹矣。朱子予以批驳:“愚谓‘见性’本释氏语,盖一见则已矣,儒者则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养而充之,以至于尽,其用力有渐,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际一有懈焉,则几微之间,所害多矣。”②指出见性本佛学术语,指证悟到佛性本空。儒者则言知性,由知性而进于存养扩充,以至于尽性。此本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儒佛之别在于:佛以见性为终极目的,见性之后更无余事。儒者则要历经由知性到尽性的长期充养扩充过程,需要在日用之间作持久的实践积累之功。佛学者虽有自命不凡,宣称见到性空者,但其人格修养、习气欲望则和常人一般,并未见其实有所得之处。张氏之说正是如此。张氏认为若诚呈现出来,则己性,以及人性、物性直至天地之性皆能呈现。朱子指出,《中庸》本言至诚尽性,而非诚见性见,“见”与“尽”意义大不相同。此不同正是儒佛所别:佛氏以见性为极致,而不知儒者尽性之广大。“见字与尽字意义逈别,大率释氏以见性成佛为极,而不知圣人尽性之大。”①
(二)戒慎恐惧:“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
张氏对戒慎恐惧极为重视,视为全篇枢纽,反复言说。仅就朱子所引52条来看,论及戒惧者即有17条之多,朱子对此痛加批评。张氏认为戒惧是未发以前工夫,使内心达到毫无私欲的状态。“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朱子则认为戒慎恐惧是已发,未发之前是天理浑然,“愚谓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②这和他以后的看法恰好颠倒,在中和之悟后他将戒慎恐惧当作未发,慎独当作已发。张氏进一步提出,通过戒慎恐惧工夫来存养喜怒哀乐之情感,以获得中和境界,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而朱子则从“本然、自然”的立场予以反驳,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乃是本然具有之中,发而中节,是其本然之和,中和是一本然状态而非人力所能为。天地位、万物育亦是理的自然发用。朱子此时承袭延平说,认为中和乃“一篇之指要”,晚年改变之,采用龟山全章乃一篇体要说。
以戒惧之说来贯穿《中庸》,实为张氏《中庸解》一大特色。在张氏看来,戒慎恐惧可解释《中庸》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如张氏认为“无忧者其惟文王”中“无忧”的原因在于:通过戒惧工夫达到无所不中和的境界;认为“博学者,戒慎恐惧,非一事也。”认为“大莫能载小莫能破”的原因在于“以其戒慎恐惧,察于微茫之功”也。朱子皆驳斥之,指出因张氏以戒惧一说横贯《中庸》全书,故屡屡造成牵合附会之病。“张氏戒慎恐惧二句,横贯《中庸》一篇之中,其牵合附会,连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①张氏如此重视戒惧,用以解释全篇,是因为他认为中庸之道正是从戒惧工夫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君子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朱子批评“酝酿”不对,盖中庸之道乃天理自然,终始存在,并非因酝酿而产生。此批评亦未见得贴切,张氏酝酿与戒慎恐惧并列,指工夫之长久义,并非形容中庸之自然。
(三)辨忠恕:“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张氏对忠恕的阐发,遭到朱子最严厉批评,成为朱子最不能容忍的解释,认为其言“最害理”。他说: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责己也,知己之难克,然后知天下之未见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②
在忠、恕的界定上,张氏继承程门之说而又有重大偏离,其肯定恕来源于忠符合程门之义,但认为忠是责己、克己,恕是饶人、恕人之说则不合程门说。程子明确肯定“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故朱子肯定无垢“恕由忠生”说可取,但对“恕”的理解有很大问题。
愚谓恕由忠生,明道、谢子、侯子盖尝言之。然其为说,与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则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为义,本不如此。③
朱子解尽己为竭尽全部心力而毫无私意,推己则是在尽己基础上推扩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絜矩之道。张氏提出,一己之私难以克除,唯有见性者方能做到完全克除己私,明乎此,故对凡未能克除己私者、未能见性者皆加以宽恕,此即忠恕义。显然,张氏把忠理解为严以责己、恕为宽以待人。朱子批评张氏是以一己之私来对待天下之人。忠恕的本质是表现为如何对待人己关系,他引张载说指出应以责求他人之心来要求自己,以爱护自己之心来爱护别人。只有抱有责人以责己、爱己以爱人、众人以望人,才能做到人我之间心意相通、彼此一致,而各得其所、各守其则。朱子指出,如张氏之说,因己私难克而容忍他人私心之存在,以至于由此而发展为罪恶之事,其后果是诱导天下人皆流于禽兽境地,完全背离了儒家忠恕之教。朱子对张氏的忠恕批评一生保持未变,①并将张载的忠恕解写入《章句》。
朱子进而剖析张氏产生严重误解的原因在于章句文义理解的偏差。张氏主张此处断为四句,分别在“父”、“君”、“兄”、“之”后断。如张氏解,则理解为子父、臣君、兄弟、朋友之间的单边关系,即深入考察儿子侍奉父亲所应尽之道,而反思自身亦未能做到。因此,未敢要求父亲对儿子给予爱护之道。朱子指出张氏断句有误,“察”字理解有误。
愚谓此四句当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绝处,求犹责也,所责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则自有所未能。……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则安敢责父之爱子乎?”则是君臣父子漠然为路人矣。……盖其驰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详,故因以误为此说。②
此处当分为八句,应在子、臣、弟、友之后点断,这种断句的差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理解,朱子理解为子父、父子双边关系,即要求儿子对自己应做的,自己对父亲也没有做到,此时的“我”处于上下交错的人际关系中,“求”与“责”是同义(而非张氏的“察”)。当由张子《正蒙》“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说来自我劝勉,推扩,而并非如上章张氏所云“因为自身私意难以克除而容忍他人之私”,这样对私意的包容必然导致人心的堕落。张氏之误源于其深受佛学用心于空虚高明之所的影响,对文本章句未加详细审查。
“当于忠恕卜之”。张氏还提出,应当从是否做到忠恕来审察戒慎恐惧的效果,即戒惧为工夫,忠恕为效用;忠恕之效用又当自父母身上审察之。盖忠恕最切近者为事父母。“张云:欲知戒慎恐惧之效,当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当于父母卜之。”①朱子批评张氏之说牵强无理,视至尊的父母为卜算之物,其说已陷入“二本”而不知。张氏显然是比喻手法,朱子过于从字面理解。
(四)诚:无息为诚、知诚行诚、注诚于身
“认专为诚”与“无息为诚”。张氏指出学者多将“诚”误认为“专”,至诚本不息,若专则息矣。语言断绝,应对酬酢皆离开本位也。“世之论诚者多错认专为诚,夫至诚无息,专非诚也。以专为诚则是语言寝处,应对酬酢,皆离本位矣。”朱子予以反驳:“专”固然不足以表达“诚”之内涵,但如张氏以“无息”为诚,亦是错误。至诚之效用是不息,而非因无息方有诚之名义也。“离本位”亦非圣人说,乃是佛老之见。此意朱子始终未变,故《章句》言“诚故不息”。
此外,朱子还批评张氏“行诚不若知诚明,知诚不若行诚大”说,提出儒家思想中只有存诚、思诚,而无行诚说。通过思诚、存诚工夫,使诚内在于己,则其所行所发皆出于诚、合乎诚。而行诚说则把诚视为一个外在于己的事物看待,造成自我与诚的分裂,完全背离了诚之意义,后果极其严重。至于诵《孝经》御贼之说,其误在于事理不明而有迂腐愚蠢之弊,与诚无关。诵《仁王经》者,乃异端之见。
张氏关于诚的效用确有许多近乎佛老的过高之说。如他指出,注诚于身则诚,于亲则悦,于友则信,于君民则治。朱子指出,若能明善则自然诚身,此是理之自然。由身诚至于亲、友、君、民皆然,此是德盛自然所至。若言“注之而然”,则认为诚身与亲、友、君、民存在距离,尚须注入之过程,已陷入最大之不诚。再如“不诚无物”解为“吾诚一往,则耳目口鼻皆坏矣”说确实怪异。②朱子提出,诚不可以“吾”言,盖诚为本体,故不必言往。耳目口鼻,亦无一旦遽坏之理。
张氏认为,诚明谓之性,是指资质上等之人修道自得而合乎圣人教化;明诚谓之教,则是由遵从圣人教化以达到上智境界者。若有上智自得而不合乎圣人教化者,则为异端。朱子认为张氏对诚明理解的偏颇,适反映出其傲然自处于诚明之境,而实际陷于异端之学。此说的目的,是想通过“改头换面、阴予阳跻”的方式来达到掩盖其佛老之迹,避免别人怀疑的目的,此恰是其最大不诚之处。其实,张氏此说意在强调“合圣人之教”的重要性,以划清与佛老的界限,朱子的理解似乎有点“草木皆兵”之意味。
“变化天地皆在于我”。至诚无息章张氏提出天地之自章、自编、自成,其动力皆在于至诚不息之圣人,天地亦因此至诚不息而产生造化之妙用。朱子从文义与事理两面作出批驳:
张氏首要之误在于对本章文义理解有差,所谓不见、不动、无为皆是言至诚之理的效用,此理与天地之道相合。张氏则以为此言圣人至诚之效用,使天地彰明变化,不仅文义不通,且不合事理。而“天地自此造化”说更加危险奇怪,颠倒了圣人与天地上下关系,若如此说,则圣人反而造化天地,推测张氏说之蔽源于佛学“心法起灭天地”之说。①
(五)知论:“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
“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张氏指出,如果做到了智仁勇,则对九经无所期待用力而九经自然得到实行,一一合乎其道。“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朱子指出此说会造成不良后果。若如张氏解,则九经皆为多余之说,张氏一心仰慕佛学高远虚灵之说而忽视了实地事为之功。
张氏指出,常人只是知道用知识去品评判断是非,而不知用之于戒惧恐惧工夫。若能“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方为大知。此说显然意在突出道德实践之知的优先性。朱子由此读出佛学的印迹,“故诠品是非,乃穷理之事,亦学者之急务也。岂释氏所称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遗意耶?呜呼,斯言也,其儒释所以分之始与!”朱子以穷理说批评张氏的移是非之心说,认为对事理是非的判断是天下正理,是一切知之开端,是人之本质和必须之当务,是行事合乎天理的必要前提。张氏完全忽视这一面,任其私知而不循天理,走向佛氏不问是非,仅求心证之途。讲求是非之知正可以作为判定儒释之分的第一标尺。有趣的是,朱子所引“直取无上菩提”与上文延平告诫朱子的“一超直入”说正好相应,可见朱子今非昔比。
张氏提出对格物的看法:“格物致知之学,内而一念,外而万事,无不穷其终始,穷而又穷,以至于极尽之地,人欲都尽,一旦廓然,则性善昭昭无可疑矣。”格物致知乃是从内外两面用功,包括内在意念与外在事物,皆要探究其终始,反复用功,达到人欲皆无的极致之地,此时心底廓然,唯有人性之善昭昭显露。由格物证悟到性善,使性善呈露彰显。朱子指出,格物当以二程之说为准,张氏之说乃是佛氏“看话头”的做法,背离了圣贤本旨,其病与吕本中《大学解》一致。
(六)章句工夫:“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
朱子在从学延平时即体现出好章句学的特点,给延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章句文义的辨析,亦淋漓尽致体现于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批评中。如前述对“所求乎子”一段的章句理解,朱子一生未能释怀,晚年还以此为典型批评以章句之学为陋的看法,提出“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的强势表述,突出了章句在义理理解中的优先性。这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章句之学于朱子而言,不是一般的文字解释,而是为学为道的工夫,是必要工夫,是首要、根本工夫。他说:
张子韶说《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点做一句。……而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贺孙。①
就短短五十二条《中庸解》来看,朱子多次指出张氏对文本的断句、字义理解有误,导致义理产生重大偏差。其中尤以“察”字的解释为有意味。除上引“所求乎子以事父”以“求”为“察”外,在“言顾行”的理解中,亦指出张氏将“顾”理解为“察”过于牵合,张氏所犯毛病在于就某一字义任意推衍,而不顾其是否合适可取。典型者如“戒慎恐惧”,忠恕、知仁勇、发育峻极等,张氏亦是将其贯穿全篇,任意使用。对费而隐章主旨的把握,“察”字亦很关键,朱子批评张氏把“上下察”的“察”解为“审察”不妥(朱子早年亦如此解),乃是“著察”义,如此才符合子思之义。张氏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已通过戒惧工夫开始致察,“察”无所不在。通过此“察”来养中和,在未发已发之间起为中和,使中和彰显之。朱子批评“起而为中和”说大悖理而不可理喻。
总之,朱子认为章句之学的疏略是导致张氏该书(学术)产生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特点的重要原因。朱子对张氏的评价是,“张氏之书,变怪惊眩盖不少矣。犹以为无有,不知更欲如何,乃为变怪惊眩哉。”①如张氏把“此天地之所以为大”释为由此可见夫子实未尝死,天地乃夫子之乾坤。朱子认为“不死之云,变怪骇人而实无余味。”②
三 阳儒阴佛思潮的“门户清理”
朱子在融汇前辈思想以建构理学学术大厦、构建理学道统之时,始终不忘“门户清理”工作,尤注意清理洛学内部阳儒阴佛思潮,认为洛学内部已经构成了一个“禅学化”集团,有其发展脉络和各阶段代表人物,危害极其之大。故该书看似针对张氏一人而发,其实具有普遍意义。
朱子以无垢为主线,清理出理学内部具有传承关系的“禅化”集团,其三个代表分别是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且愈往下其禅学程度愈深,表现愈明显,危害愈大。朱子指出上蔡入佛的表现主要在以知觉言仁,认为见心即仁,把心与仁直接等同起来,违背孔门之义,是由儒入佛的一大转向。其思想尽管隐秘,其源头乃分明是禅了。上蔡禅学程度尚轻,尚在儒学门户之内,不敢与儒学决裂。到了张九成,则又更进一步了。张氏亦主张以觉言仁,并变本加厉了。与谢氏不同,张九成有确切的佛学师承,拜师大慧宗杲,并深得其器重,因其气质豪雄粗疏,故与宗杲非常投缘。张氏大胆采用禅学,与儒家之说公然相冲突亦不顾,争夺门户,惑乱人心。张氏作为士人好佛的名士,树立了坏榜样,还把当时另一名士汪应辰引入佛门。集宋代士大夫佛学真正大成的则是陆九渊,其对儒学的背离又远在前人之上。朱子在未与陆氏兄弟(子寿、子静)见面前,便风闻二兄弟学宗张氏①,内心颇为不安。越到晚年,尤其是与陆氏学术对立日益明显之后,就越加笃定金溪之学就是禅学,是真正的禅学,并根据自身学佛经验现身说法,指出张拭、吕祖谦因未学佛的缘故,未能看出陆氏之学的要害,其实只要看看相关佛经如《楞严》等,陆氏佛学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陆氏之天分、口才,影响皆较前者远甚,且与朱子同时,故成为朱子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病。
(盖卿录云:孔门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一转云云)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张子韶出来,尽冲突了。近年陆子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方子。②
又说张无垢参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后来亦好佛。③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④
朱子选择张九成作为突破口,试图端正“禅者之经”的学术倾向,用心良苦。张九成人品高洁伟岸,学有渊源,曾问学于杨龟山,是二程学派的传人,为南宋初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⑤且张氏“以禅解经”的著作当时很受欢迎。朱子非常警惕“内部人士”“禅者解经”的佛化倾向,它表明佛学思想对儒家侵蚀极深,危害极大。故直接将张氏说判为“洪水猛兽”,以突出其对学者心灵的巨大负面作用。朱子视张氏为“禅者解经”的代表,这种“禅者”不是信佛僧人,而是佛化的儒家学者。“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①朱子对张氏“可怪”之说一向秉持拒斥、消除态度。对其著作在浙江之刊行数次极表忧虑,盖其著作是“坏人心之甚者”,深惧其贻害无穷。并由此反思自身当加强对儒学的研讨,以救其祸害。
近闻越州洪适,欲刊张子韶经解,为之忧叹不能去怀。②
闻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学浅,又未有以遏之。③
比见婺中所刻无垢《日新》之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无力可救,但窃恐惧而已。④
朱子发明“无垢句法”一词来概括张氏以禅解儒、凭空杜撰、“脱空狂妄”、肆意想象、无济于事的解经风格。⑤“无垢句法”作为一专有名词,朱子常用以警示弟子。指出这种错误不仅是文义理解问题,且关乎思想的根本走向,是不可容忍,必须改正的。由此形成一种“辟无垢”的氛围。如批评林择之“同一机者”之说“颇类无垢句法”。⑥且朱子弟子中确有张氏的崇拜者,他们甚至不满于朱子对张氏的批评,尤其在早期弟子中。如许顺之即是如此。朱子在给许氏的信中要求他以张氏之学为戒而不是为学。“如子韶之说,直截不是正理……此可以为戒而不可学也。”⑦即便对得意高弟如吴伯丰、陈淳,只要解释稍有过高之处,朱子即以“无垢句法”告之。“此段大支蔓,语气颇似张无垢,更宜收敛。”①对于初次来学者,朱子则会了解其学术背景,主动询问是否受过张氏影响,可见朱子对此之重视,这与朱子关注问学者是否从学金溪相似。如窦从周初见朱子时,曾问起之。“问曾看无垢文字否?某说亦曾看。问如何?”从周。②
朱子对无垢以禅解经的实际案例时刻注意抨击。如指出其解释孟子四端说“犹是禅学意思,只要想象。”对其《论语》评论较多,指出多有与上蔡相同处,如有学者问,“张子韶有一片论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说亦然。”大雅。③朱子指出张氏认为佛氏有形而上而无形而下之说非常可笑,割裂了道之体用。“顷见苏子由、张子韶书,皆以佛学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尝窃笑之。”④特别是批评张氏“事亲体认”说陷入“二心”说,实为禅学之当机认取,使事亲事兄的意义工具化,仅成为体认仁的手段。
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僴。⑤
总之,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辨析紧紧围绕文本字义与义理解析展开,尤为注重揭示《中庸解》的佛老因素。朱子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对文义的把握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章句文字之学,而是把握思想义理的首要之关。无论是思想的正面建构还是反面批驳,皆须先从文义入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朱子的为学工夫中,章句之学是其首要之门,与西方逻辑分析之学亦有相通之处,故应提高对其意义与价值的重视。对张九成的批判亦集中展现了朱子从学延平后这一时期的《中庸》水平,显示了与其后期成熟思想的延续性和差异性,真实记录了朱子思想发展的阶段特质,堪称朱子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朱子在辨析中熟练运用大量佛学术语批判对方,体现了朱子对佛学的认知掌握,显示出对佛学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思想自信。可见,辟除理学内部“禅者解经”的清理门户工作,与吸收前辈思想开展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于朱子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朱子通过对《四书》的诠释,开创了新的经学时代,即四书学时代。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功,在于赋予了四书新鲜血液,将其诠释成一个崭新的经学系统。此一新经学系统既不同于原始形态的四书,亦不同于汉唐实证背景下的经学化“四书”,而是在宋代理学大背景下孕育而出的义理化四书。此一义理化四书学内容丰富,其中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牢固树立了儒家的道统思想。朱子在四书学中提出“道统”二字并予以深刻阐发,使道统成为儒学基本范畴,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节在参考时贤成就的基础上,拟从四书学与道统、道统、学统、政统之关联、“十六字心传”、道统说之形成几个方面对朱子四书学之道统思想作一探讨。
一 四书学与道统
朱子四书学与其道统说关联甚紧,二者关系可概括为:因《四书》以明道统,明道统以率《四书》。在诠释四书的过程中,朱子提炼出道统这一创新概念,以证明儒学之道绵绵不绝,足以抗衡佛老,化民成俗。道统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四书作为传道之经这一性质的点醒。
四书学是道统说的理论来源和存在根据。从道统传道人物来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记录、传承他们思想的经典相对应,对四子思想所代表的儒学道统的理解认识,必须经由此四部经典而获得。在朱子看来,自孔孟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儒家之道蕴而不彰,没有得到有效传承,仅仅存在于言语文字之间,直至二程始从传承此道的四书中重新体悟出儒家之道并接续发扬之。由此肯定传道经典与发明儒家道统一体相关,密不可分。道统来源于圣贤之经典,亦显示出其道之有统的存在根据,故能传承越数千年之久,超越时空局限。
朱子道统思想源自对四书思想之提炼,构成贯通四书学的一条主线。表面看来,朱子道统思想取自《尚书·大禹谟》,然其实质内涵“天理”“人欲”,则为朱子四书所反复探讨之主题,其传道谱系亦早已存在于其中。如朱子说:“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①。尧命舜的“允执厥中”说《论语·尧曰》章为“允执其中”,《集注》全引杨时语以阐发孔孟传道之意:《孟子》末章,《集注》亦阐发其道统接续传承之意:
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②
朱子认为道统之传有赖于以四书为主的经典文本,经典文本在传播道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子思作《中庸》一书即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及平日所闻父师之言,以昭后之学者。故该书在“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方面,极为突出,“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这和陆九渊的心学、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悟本心相区别开来。陆九渊认为不识一个字亦可堂堂正正做个人,这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自然是可以的。但如要成为圣贤般的人物,要使个人各方面素养得到全面提升,就离不开对经典的涵养体认。二程之所以能在千年以后接续道统,也正是借助了《中庸》这部经典,“因其语而得其心也”。子思传道之功正体现于《中庸》一书,二程兄弟透过该书文字而领悟圣贤传心之妙,“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
二 道统、学统、政统
朱子提出的道统说,包蕴政统与学统之义。于朱子而言,为道、为学、为政本即通贯一体,如此方为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章句序》指出,道统之传来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上古继天立极之圣神”,此五位实为两个阶段:圣神所代表之阶段和圣王所代表之阶段。目前所能见到有经典记载者,则始于圣王尧舜。朱子为何将道统推至圣神阶段呢?学者解释其因在于伏羲的易学太极说对朱子理论体系甚有影响,但如何解释“神农、黄帝”呢?窃以为,恐怕还是为了加大道统的历史时长,树立道统的权威性,以对抗佛老。这种久远,神秘的人物,总能带给人一种神圣的崇高感。朱子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就将伏羲置于道统的源头,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这个“远”字就透露出些微消息。
道统的开启者同样是学统、政统的开启者,原因在于他们同时兼具君和师双重身份,《大学章句序》中称他们是“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故“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在那种政教合一时代,他们即是道、学、政的统一。学统是道之得以有统的必要手段,它的发展与道统紧密呼应,二者实为一皮之两面。三代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两级教学体系,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一穷正修治之道,即精一执中之道。学统之发展和道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大学章句序》说,孟氏之后,学统失传,“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学统让位于无用的记诵词章之学、无实的异端虚无之学,而且还遭受到功利权谋之说,百家无端之言的有力冲击。这些学说的纷纷涌现,使得儒学之道湮没不明,丧失了在思想界所具有的话语主导权,失其了对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即道学不明,道统失传,治道不彰,政统失效。直至在“治教休明”的宋代,二程先生才上接学统,使《大学》经传之旨复明于世。
尧舜禹汤文武是圣圣相承之过程,是道统和政统相统一时期,为儒家大道得行、内圣外王相统一时代,属于常理的“大德必得其位”。自孔子以后,转入圣师时期,德位分离,道统和政统开始脱离,故儒学转向强化道统和学统的合一。朱子认为,孔子所渴慕者仍是帝王之治,他在《论语》“何如斯可以从政”章注引尹氏说,“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①孔子不得其位并没有妨碍他的成就,他反而因继往开来之贡献越过了尧舜,孔子是以学统的形式延续了道统,他深入阐发内圣之学使道得以彰明,使借助学统形式所表现的道统依然保持了其独立性和超越性,发挥了对势的抗衡和宰制。这一抗衡是经由道统、学统领域转至对政统的重建而实现的。在这三统关系中,道统与学统密不可分,而接纳政统也一直是道统的应有之义。故《中庸章句序》即明言传道即是传政,“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诫,不过如此。”《语类》对《论语》的评价亦表露此意:“《论语》后面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之类,皆是恰好当做底事,这便是执中处。尧舜禹汤文武治天下,只是这个道理。圣门所说,也只是这个。”②朱子强调道统传至孔子是一个转折,进入“不得君师之位”的阶段。意味着道统不能再在高位顺畅下行,只能在学统的低位轨道中曲折前行,其主要任务是肃清思想界的异端庞杂之说,确立儒学在思想层面的地位。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在政治层面的抱负,而是通过道、学对君王产生影响,使之接受儒家政治标准而间接推行其外王。故此,朱子在政治上的最大主张和努力,即是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其武器即是精一执中这个道统,希望帝王接受儒家的道统说,由王而圣,恢复三代时候的圣王合一。这在朱子给皇帝的《壬午封事》、《戊申封事》中表露得极其明显。朱子与陈亮关于义利王霸之争,亦是从道统的高度来看待政统,他认为三代与汉唐的差别不在乎尽道多少这个量的问题,而是在于道之有无这个本质问题。以道观治,千五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代、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①。以此观之,这千五百年的政治与儒家之道并无多少关系。“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种偶合,其根本是功利霸道之治,于尧舜三代之王道仁义之治,根本不类,“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反诸王道之治,“莫若深考尧舜相传之心法,汤武反之之功夫,以为准则而求诸身”。②
朱子的道统说是对儒学发展的历史总结,尤其是对自宋以来儒学内部纷扰局面的整合,抵抗了佛老等对儒学的冲击破坏,指引了儒学发展方向。在北宋诸派纷争时,各家都展开过“一道德”的工作,试图统一儒家自身内部的思想,来对抗佛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朱子之前,这项工作并未完成,朱子提出道统二字即是为了作一次正本清源的工作。“道统”一名实自朱子首倡。③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朱子为何用“道”而不是“仁”或“理”这样的名称呢?孔子之学是成仁之学,一般概括为仁学而不是道学。朱子却说“子思忧虑道学失传”,采用“道学”二字,其考虑何在?④朱子用道学来概括儒家之学,一方面是看到了儒学的延续与发展、同一与差异。在孔子,道的核心为仁,工夫表现为忠恕、克己;在孟子,道的核心为仁义,工夫表现为存心、养气;而在二程,道的核心则为理,工夫表现为格物穷理,居敬涵养。更主要的一面则是“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所指包括儒家内圣外王之两面,《中庸章句序》就透露出这个道兼具道统、学统、政统的三重意味。
三 “十六字心传”
朱子道统说主要有两方面:传道谱系和“十六字心传”。
在道学得行的上古三代,道无需特别传扬;至道不得行之后世,则必须由专人传扬。孔门颜曾传道学宗旨,由曾氏再传至子思、孟子。在子思时代,不仅政统早已失去,连道统亦受到异端威胁。出于对道统失传的忧虑,子思写下《中庸》一书,然道传至孟子而终失其传,此后千载为异端“日新月盛”时代,特别是佛老,“弥近理而乱真”,直至二程兄弟,才通过对《中庸》的考察研读,接续子思之传,倡明圣学。然二程之说又“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朱子特别点出对二程弟子之不满,说他们所自为说“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故朱子以强烈的道统继承感,自认为二程之学的接续者,承担起阐发道统的任务。朱子道统谱系特点是越过汉唐千年岁月,将对儒学发展颇有贡献的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剔除出道统之外,认为他们没有真正领悟儒家道统之精髓,对儒家之道存在程度不同的偏离。同时,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亦没有将周敦颐、张载及他所传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列入道统。这是因为尽管朱子对道南学脉这一系抱有相当的尊敬,但是亦批评他们“静中体验未发大本”的工夫有所偏颇。尽管朱子对周敦颐、张载很是推崇,但就《四书》传道而言,二者似留意、发挥不够。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作为儒家道统说的核心,定下了道统说的基调。此一道统核心主要包括“允执厥中”的目标、“惟精惟一”的实现工夫,这一工夫之关键在于精察人心与道心之别。
朱子道统说的目标是“允执厥中”,此四字即是尧之授舜的心法,“尧当时告舜时,只说这一句”①。朱子认为,尧之授舜,本来仅此一言就“至矣,尽矣!”“舜复益之以三言者”,不过是“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即后面三言是实现“允执厥中”这个目标的方法。朱子提醒学者,执中之执为虚说,是“无执之执”,因为并没有一个作为实体的中来被人把握,“执”只是心里默自用力,不失中道。若能获得中这个天下大本,随时处中,使日用思虑动作恰到好处,那在道德成就上就达到了中庸之境。中作为一种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它表现出来就是无处而不自得,就显现为一种方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朱子认为它是舜告禹时所添入的。“后来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①这三句即表明了如何达到中这一至德的工夫进路。“这三句是‘允执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处。”具体而言,它有两个向度:“精”之察识与“一”之操存。在《中庸章句序》的第二段,朱子详细阐述了这一工夫过程,并对这一对概念有着详尽说明。
人心之危。心实质上只有一个,即表示价值中立、强调属性功用的虚灵知觉之心,它包括人的感性欲望和知性思考。“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虚,是心处于不作价值判断的虚空状态;灵,指心的流动不居,变化作用的活动态;知觉指心的感知、判断能力,这些皆是心所本有之特点。人心和道心则是从道德价值角度作出的区分。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指个体所必有之感性需求,其特点是“危殆而不安”,原因在于“人心易动而难反”。由形气所构成的物质躯壳为人人所私有,决定了其欲望之满足皆是不可公约的一己之私。故与此形气相连的感性欲望是危险的,容易滑向欲望的泥沼。“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②但人心之危并不代表坏,并不表示要舍去之,只是要唤醒人们对欲望之私的警惕和节制。“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个不好底根本。”正是因为形气属于个人私有,私欲、私念、私心就皆从此气而出,是一切私之根源。视身体为一切私欲的根源,是诸多学派的看法。人心对于道心而言,并非不好,其在道德价值上是中立的,可善可不善。只是因受到物欲引诱污染,人心才走向不善。朱子以圣贤亦不可无人心形气为例,说明二者并非不好,肯定了人基本需求的正当合理。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人欲才是不好,才是恶。因此,朱子特别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他指的人欲,即是人之私欲,是超出正常要求的需要。朱子对此有很明确的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③
道心之微。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构成人的超越面,指向人的价值善。特点是微妙而难见,“义理难明而易昧”。朱子认为心具道心和人心之两面,道心是义理之心,人心是血气之心。“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①道心之“微”既指精微难以捉摸,又指隐微难以发现。凡是精细之物皆隐藏在内,不易发觉显露,道心亦然。道心虽然先于人心为人所得,但人心与人的关系更为贴切,故道心往往被人心所阻隔,好比清水之混于浊水也。朱子还从人需求的三个层次来分析道心难见的原因,第一层次是生理上饥寒饱暖之类的欲望,极其明显而容易感觉,故人人皆知之;第二层次是算计谋划、趋利避害等较为精细深刻的需求,某些动物对此没法感知;第三层次是纯粹精神上的道德感受,只有人才独有,是人真正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的道心即是第三层次道德需求的反映,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故并不像反映人基本欲望的人心那样遍在呈露。“天下之物,精细底便难见,粗底便易见。饥渴寒暖是至粗底,虽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较细者言之,如利害,则禽兽已有不能知者。若是义理,则愈是难知。”②
朱子对人心和道心关系做了多角度的比较,以下观点值得重视。
人心和道心是相对性概念,判定的根据心之价值指向是理还是欲。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单独说人心,皆是好。只有当它与道心相对言时,才凸显了它不好而容易流于不正的一面。“有恁地分别说底,有不恁地说底。如单說人心,则都是好。对道心说着,便是劳攘物事,会生病痛底。”④
道心应对人心起主宰作用,即以义理为准绳来制约人欲,这样才能“允执厥中”。《中庸章句序》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构成人心的知觉欲望若没有主宰定止之物,容易放纵陷溺,危而难安;道心是义理之心,具有主宰约束功能,故可以为人心之标准。朱子用船和柁的比喻来表明道心对人心的导向作用,来自于形气之私的人心在善恶的天平上中立两可,正犹如漂荡于水中无所定向的船,必须以道心为主宰方能为善;反之,交付于形气,就失去目标和方向,则是恶。“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①朱子还从气质之心的角度论述人心可善可恶,道心则内含天理。“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②朱子认为,形气是物,道心就是则,有了公共无私之则的控制,那么形气之私就可以存在。这和胡五峰的“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是相一致的。人心和道心为所有人之共有,圣愚的差别在于以道心为主还是以人心为主。人心为人生来即有之本能,实不可无,强调人心、形气之客观存在,为人内在先天所本有,这是儒家和释老的一个区别所在。朱子指出,即便是大谈空虚之道的释老,也无法摆脱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人心终不可泯灭,且在存在上先于道心,它关乎人的现实存在。“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然则彼释迦是空虚之魁,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③
道心和人心的对立,与天理人欲、公私这两对概念相对应。道心对人心的宰制,也即是使“天理之公胜夫人欲之私。”“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④朱子在此采用二程之说,直接以天理和道心,人欲与人心画上等号。因为道心本来即含天理,人心本来即含人欲,故以理制欲,即是以道心制人心。朱子同样认为,道心与人心亦可视为公和私的关系,天理是天地万物公共之理,人不得而私;人欲则是从个体躯壳上发出的需求,为人所私有而不可公。朱子由此将人努力要达到的允执厥中的目标转换为使天理之公战胜人欲之私,即存天理灭人欲。存得一分天理,便灭得一分人欲。可见,这个人欲实质指人之私欲,并非所有欲望,合理欲望乃是不可绝灭的。“大概这两句,只是个公与私;只是一个天理,一个人欲。”⑤人心和道心本为一心,人心显明易见,道心隐晦幽闭,通过努力做工夫,可以到达道心和人心合而为一的状态。这个合而为一不是消除人心,而是使道心全部在人心上呈现,化人心为道心。于圣人而言,即是如此,圣人浑身皆是天理道心。“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都发见在那人心上。”①“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这种人心和道心的合一关系,需历经艰难的工夫实践方能达到,而且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正因为人心道心其实只是一心,上智与下愚皆兼具此二心,故圣凡之别只是在于道心与人心量的多少,而非质的差异。这就使得圣凡的差距缩短,肯定二者在人性上的同一性,许诺了即凡而圣,下学上达之可能,亦是对“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阐发。
人心与人欲。朱子哲学是复杂的思想系统,如何区分人心与人欲的关系,也是朱子思想中一个不易分清的问题。朱子在此问题上思想处于变化之中,早期采用二程的“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视人心与人欲在此语境中意义相当;后则有“‘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说,主张区别人心与人欲。但此前后期的人心与人欲的等同、区别亦是大概而论,朱子亦可能存在人心包含人欲,人欲为人心之欲望的看法,即二者类似于上下位包含关系——人心含知觉、嗜欲两面,皆其所不能无。“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大雅。②其实,在理学(朱子学)话语系统中,理与欲、理与心是相对的两组范畴,心与欲并非相对的范畴,而更多被视为一种等同关系(二程、早期朱子、阳明、甘泉)或包含关系(中晚年朱子,私欲之心、欲望之心)。故此,我们在理解朱子关于二者用语时,应保持情境、动态、相对的看法。对于朱子在具体时机下提出某种与其定见不同的说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能就此判定该种说法一定是错误的,若如此处理,将导致对朱子思想成熟的复杂性、艰巨性的遮蔽。《语类》的记载,当然存在问题,编者已经标注不少说法与《集注》不相应的“问题语录”,如“记者之误”“传写之误”“记录有误”“此言盖误”“《集注》非定本”等。
以下讨论朱子的人心、人欲说。
1.滕璘辛亥(1191年)所录,朱子肯定伊川人欲人心、天理道心说。“方伯谟云:人心道心,伊川说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可学录别出。①
2.郑可学戊申(1188年)所录,朱子肯定人欲便是人心说。“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②
3.张洽癸丑(1193年)所录,朱子称赞程子人心人欲说穷尽心传之旨。“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此言尽之矣。……圣人心法无以易此。”③
正因人心即人欲,故人心之危亦可谓人欲之危。
4.“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如何谓之危?既无义理,如何不危?”黄士毅录。④
5.“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坠未坠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董铢录、潘时举录同。方子录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辞”。子静说得是。⑤
朱子去世前一年己未(1199年)吕涛所录《语录》明确提出“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⑥。可见并非人心可言危,人欲也可言危,其危表现为陷溺。这种意义下的人欲与人心相通。
第4条语录,朱子明确分别了人心、人欲、道心。朱子起首即说,“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接着以饥食寒衣之基本欲望为证,指出就通常意义而言,这种人欲并非不好,只有当它与义理相脱离的情况下才是不好。人心是心灵的知觉功能,在价值上中立,决定价值取向者在于知觉的内容,在对待的意义上,人欲与道心代表知觉的善恶两端,人心既非人欲,亦非道心,而是包含二者。就此条语录之特定语境,可知“人欲”概念包含在“人心”中,是人心的一个方面,指人心之欲望。人心与人欲并非对立,而是包容关系。故提出“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朱子屡言人只有一个心,道心、人心皆是一心所发。人欲与天理一样,皆是人心应有的必要内容。陆王之学,突出人心天理一面,完满自足。朱子更关注现实欲望对人心的腐蚀,强调道心主宰人心的功夫。朱子对人心的描述,往往就其必要欲望而言。本条语录中人欲指对饥渴等生理需要的欲求之心,对饥渴的欲求连主张四大皆空的佛学都无法否定。在朱子看来,这种欲望其实即是天理,“饮食,天理也。”朱子的理、欲范畴是在特定意义下,具体语境中相对而言,对其具体指向必须具体分析。本条语录的三句话是一个关联整体,每句各有指向,分别指向人心、人欲之心、义理之心,构筑成一个内在语义圈。第一句总说人心不能武断为不好,第二句以反问语气指出对饥寒的欲求之心符合人的正当需求,不能就此断定其为危险,意在强调此种人欲的必要合理性。第三句为第二句之补足,同样以反问语气指出即便是必要合理的欲求之心,若无义理为之主宰,难保不会走向危险之路,故必要合理的人心、人欲,也需要道德之心为其主宰。
第5条语录讨论程子的“人心,人欲”说。问者提出程子“人心,人欲”与“人心惟危”说相冲突,认为人心“恐未便是人欲”。主张人心可善可不善,人欲则全不善,二者不可等同。朱子回答切中要害,言:“人欲也未便是不好。”即人欲与人心一样,也是危而不安,不可直接称之为恶。朱子对人心与人欲关系的看法源于二程,伊川对此的经典表述是“人心,人欲;道心,天理”。分别以人欲、天理解释人心、道心。这种惟危的人心就是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应当克除之。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二程外书》卷二)①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德,一作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③
二程有的表述将“人欲”替换成“私欲”,道心表述为“正心”。这种表述更见准确,区分了此语境中的人心特指人心欲望中的私欲,此“私”不是从身体言,而是从道德上判定,此私欲“危殆”,需灭除之,以明天理。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二程遗书》卷十九)④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遗书》卷二十四)⑤
从发展眼光来看,朱子对程子人心、人欲之说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前,朱子采用二程之说,将人心与人欲、道心与天理并提。如《观心说》“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在晚年形成独立看法之后,对二程说并未完全抛弃,而是仍有肯定。如上所引滕璘、郑可学辛亥所录、张洽癸丑所录问答,朱子皆分别以“固是”“然”“尽之矣”充分肯定程子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在与郑可学的讨论中也肯定天理道心、人心人欲分别说。朱子反复指出,人只有一个心,心是理气结合体,天理、人欲皆在此心中,皆由此心发出。心具有知觉功能,觉于理是道心,觉于欲则是人心。人欲与人心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这样就把理欲分别得很清楚,所以朱子称赞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和五峰说“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说。
晚年一般情况下,朱子对程子“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说不乏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要强调人实质上只有一个心,担心程子说分别过度,有分成两个心的嫌疑。反复指出道心与人心的分别取决于知觉的方向,觉于理是道心,觉于声色嗅味的感官欲望是人心。特别强调,以感官欲望为主的人心必不可少,也并非不好,只是危险而已。如果全是不好,则人根本无法树立道心为主的道德主体。①为此他反对“人心人欲”等同说,因为即便是圣贤上智之人,也离不开人心。如果把人心等同于人欲,就有把人心视为全部不好之意,有消除人心之意。朱子在此显然是从狭窄意义上,即与天理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人欲,认为人欲是个否定性的词,不可与人心混用。这一说法仅见于此。事实上,朱子对人心、人欲的关系存在对立或包容两种看法。当认为二者对立时,则否定人心人欲说;认为二者包容时,则肯定人心人欲说,这取决于对人心、人欲的理解。如朱子认为圣人纯是天理毫无人欲,但圣人也有满足饥渴的生理需要,此类生理欲望朱子解为人心而不是人欲。
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萧佐甲寅所闻。②
总之,对朱子人欲说应具体细致分析。当朱子单独说人欲时,人欲所指较广,在价值上中立,可善可恶,是必须而不可以消除的。人心来源于形气之私,形体的存在必然有人欲,如我欲仁、饮食饥渴之类。当与天理对说时,则是狭隘义的人欲,指过分的不合理的欲望,是不应该存在的。朱子人欲说与现代人的理解存在一个很大差别,即对必要的饮食生理欲望性质的判定,需要根据其对象、数量、场合等因素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它实质上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单纯的事实概念。朱子常以天理人欲相对,学者问饮食这种人人皆有的欲望到底属于何者,朱子当即肯定,一般意义上的饮食之欲属于天理,而对于超出要求的美味等欲望,则属于人欲。其实,饮食与要求美味皆是欲望,二者差别在于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的关系。饥渴之欲本身无价值判定,决定的根据在于欲望的度,这个度需要个体根据具体情境来把握。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甘节癸丑以后所录。①
朱子常以“分数”“界限”表示此度,这个度决定了欲望的性质。就此意义而言,天理和人欲是一体的,“同行而异情”,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也有天理。只是过分了,侵占了天理的界限。故对此度数、界限需要严格把握,这也就是天理人欲的相对之意。
即便满足生存的最基本的饮食之欲,也不一定是必需的,是合理的,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场合来决定。如嗟来之食,尽管数量甚微,且为生命所必须,但必须拒绝之,以维护天理大义。由此可见,朱子的理欲观,并没有坐实具体事物,饮食等具体欲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如佛家非善非恶的“无记业”,只有当其过度或与道义发生冲突时才能做出道德善恶的判断。判定的尺度在于内心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故此,理欲只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其落实需要就具体情景而言。朱子有时称饥渴是人心,有时称为天理。可见,饥渴既可以是人心,人欲,也可以是天理,道心。抽象孤立的饥渴在道德上没法判断,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判断满足饥渴方式是否合宜。因此,朱子称人生只有天理,人欲是后天之物,是从天理之中产生,是对合理欲望的过度。
问:“饥食渴饮,此人心否?”曰:“然。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①沈僩戊午1198年以后所闻。
“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黄榦录。②
在《孟子集注》“养心莫善于寡欲”章,朱子同样指出耳目生理的欲望,为人所不可缺少,关键在于是否受到节制,这直接决定了本心是否受到蒙蔽。“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这个不能无的欲并不是恶,在价值上中立。总之,朱子关于人心的论述,皆是以人欲为立足点。耳目之欲为主宰则是人心,义理为主宰则是道心。故道心、人心之别亦可谓天理人欲之分。
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复杂性与他对二程“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说的前后态度有别相关,故其后学高弟黄榦、真德秀皆强调当区别程朱人心人欲说之不同。“若辨朱程之说不可合一,则黄氏乃不易之论也。”③还指出,“欲”字单言,并无恶义,只有在天理、人欲相对时,才表示恶。而且,即便“私欲”亦非是恶。
盖“欲”字单言之,则未发善恶;七情皆未分善恶,如欲善、欲仁固皆善也。若耳目口鼻之欲,亦只是形气之私,未可以恶言。若以天理、人欲对言之,则如阴阳昼夜之相反,善恶于是判然矣。朱子“形气之私”四字,权衡轻重,允适其当,非先儒所及也。或谓私者公之反,安得不为恶?此则未然。盖所谓形气之私者,如饥食渴饮之类,皆吾形体血气所欲,岂得不谓之私?然皆人所不能无者,谓之私则可,谓之恶则未也。但以私灭公,然后为恶耳。……愚答之日,私者犹言我之所独耳,今人言私亲私恩之类是也。其可谓之恶乎?又问六经中会有谓私非恶者否?愚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如此类以恶言之,可乎?其人乃服。①
总之,朱子的人心是以知觉、欲望为主的。其人欲说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不当有的欲望。这个“人欲”是与天理对言时的特定意义,或以“私欲”出之。《集注》“人欲”说共有30余处,除一两处因行文关系外,其余皆天理、人欲对说,主旨是“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此外“人欲之私”的说法有12处。可以说,人欲在朱子那里是与天理相对立的概念,代表了否定面,与人心不可等同。但是单独言“人欲”,则并没有反面意。朱子对程子说的不满意,在于要肯定饮食等基本欲望,而不是否定。如照其人心人欲说,则饮食基本欲望无法安顿。程子说的最大问题在于道心与人心相对立,不可并存,但道心、人心却不是消灭关系,而是主导、化解关系,朱子必须给包含基本欲望的人心留一个空间,以此批评佛老之说。
惟精惟一之工夫。确保道心对人心统领的工夫落实在精察和持一上。若没有适当工夫对二者进行简别,那么将会使本来就危殆不安的人心更加危险,隐晦难见的道心更加隐晦,天理也将无法战胜人欲,道德的成就将不可能。为此,须要展开精一之功。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道德性命和生理私欲共存一体,相互夹杂。正是因为二者相即不离是人的存在之本真状态,故精心辨别二者,在知行上同时用功,谨守道心以宰制人心,以确保二者界线的不相混杂,就非常重要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困难在于危殆不安的人心时刻给予道心强大的刺激冲击,使人的行为偏离道德的轨道,造成微妙难见的道心之遮蔽;要想做到使人心受道心的约束,需要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努力修习过程。《中庸章句序》中说,“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精即是知上察识工夫,它强调精确鉴别天理人欲、道心人心,避免二者相互混杂,以保证道德的纯粹性;一即是行上操存工夫,它要求始终如一的专注于此,保持本心的中道不偏。而且,工夫不能有丝毫的间歇停顿,以便化人心之危为道心之安,使道心之隐微呈露昭彰。朱子从知行两方面分别精一之功,要求知行并进,专一用功,特别突出“惟”字的重要。朱子对精和一的范围、界线进行了划分,如学问思辨皆属于精察工夫,笃行才是唯一的行上工夫;在知上明了,还须在行上实之,才能落到实处。在精一关系上,精作为知上对善的抉择,在工夫次序上优先于行上的执持。“择善,即惟精也;固执,即惟一也。”真正做到精察的前提在于内心的“虚明安静”,排除纷杂意念的干扰,保持内心的澄澈空灵。“一”就在于内心的“诚笃确固”。朱子提出精一的知行二者乃互补互动关系。“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在惟精惟一的操作上,朱子也指出几点:其一,不仅在心上,还要在事上下工夫,工夫应贯穿于日用动静之间。他特别强调事上工夫,实处下手的重要。提出心和事的对应,即思想与行动的一致。因为道理便在日用间,所以工夫也自然在日用间,这是针对佛老工夫空虚而言的。“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①其二,因为人心道心关系极其微妙,故精一之功关键在于二者未发已发之交界处。人心和道心的差别仅仅是一条界线,二者之相互转换极为容易,稍不留意即滑向一边。由此更加强调知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只有明察了理欲之别,才有可能专守道心。“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②“人心道心,且要分别得界限分明。”③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思想的形成历经一长期过程,学界对此亦多有讨论。此一道统形成过程与朱子思想成熟相同步。简略言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拜师李侗时,注重十六字心传的政治教化义,将之视为帝王必修之学。据《壬午应诏封事》可见此时朱子道统思想尚不成熟:将尧舜禹混在一起,并没有分成两个阶段,而在《章句序》中,则说尧舜相传以“允执厥中”这一言,其他三言为舜禹相传时所补上;以《大学》致知格物和正心诚意分别解精一和执中,未能细致区分工夫和目标关系;在《章句序》中,致知仅仅属于惟精工夫,惟一属于力行工夫,而正心诚意也并非执中。“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要求孝宗“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①。
中期是在确立中和说之后,朱子对道统说有了新的认识,奠定了后来道统说的基础。朱子在辛卯(1171年)的《观心说》中提出了天理人欲,人心道心说,指出人只有一心,这些皆与他后来思想一致。但是不足处也很明显,没有提出道心和人心的来源及其特点,没有在工夫论上对精一作出分别,而且直接以心之正与不正区别人心道心,亦有不妥。“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②甲午年朱子和吴晦叔讨论人心私欲说时,反思己说“人心私欲”不对,原因在于未能察识本源,惟精惟一工夫的前提即在于知上察识本体,然后加以精一工夫。精一工夫是个长期过程,其中亦有等级进步处,并非能一蹴而就,并特别强调尧舜所谓人心私欲和常人不一样,它仅仅是稍微的走失和不自然。
后期是丁酉(1177年)朱子四书学初成,思想大体定型后,道统说亦进入完善期,此一阶段最后定见则是《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在此期间,朱子透露尧舜相传一段乃是丙午(1186年)所添入,“《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③。在早于《中庸章句序》一年的《戊申封事》中,朱子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十六字心传道统说,和《章句序》的差别仅在个别字词。如“人心、道心之别,何哉?”(《章句序》将“别”改为“异”,无“何哉”二字);“或精微而难见”。(《章句序》中改“精微”为“微妙”)。
尽管道统说为朱子所提出,但亦有其理论渊源,受二程影响尤其深。如二程提出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说,指出天人本是一体,但现实之人则存在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之别,要求以精一工夫灭弃人欲存得天理。当然,朱子道统说亦自有创见,如将《尚书》十六字心传和《中庸》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
朱子道统说常为后世诟病者,除传心说形式上近佛外,最根本的则是“十六字心传”的真伪问题。据历代学者考证,尤其是清代阎若璩的考证,证明此十六字出自《伪古文尚书》。据此似可推翻朱子所苦心经营的缘于上古的心法之说。其实不然,汉学家虽可以证实朱子所用这一条材料为伪,但是作为道统的关键,执“中”思想,的确已经在上古文献中存在。而且,朱子围绕“中”展开的儒家传道说,侧重点在于周公、孔、孟、二程,上古尧舜授受之说为后来所添入,在其中仅仅起到引子的作用,即使割弃之,其道统说亦足以成立。故否认这一段文字,并不能否定以执中为核心的道统思想,只是采用这十六个字能更好地为其理论服务而已。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是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此后儒家道统说之正统,意义重大。它是对数千年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次总结,通过对道统谱系的梳理,确定了颜曾思孟、二程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指明儒家侧重内圣之学兼顾外王之业的特点,为儒家学者提供了价值认同模式和参照标准。
第二节 孔颜克复心法之传
朱子道统说虽以“十六字心传”为根本,然此并非朱子道统思想之唯一表述。事实上,以颜子为代表的“克复心法”在构筑朱子道统学中亦具有其不可忽视之地位。朱子虽于《中庸章句序》言当时传孔子之道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但因颜子早逝而无著述,故其在道统中的地位多不为学者注意。有论者表达了疑惑,“道统之传未列颜渊也令人不解”。①仔细考察朱子道统说,可知颜回在道统中的地位非但未失落,反而得到有力阐明。朱子“克己复礼为仁”章注从“心法”的视角对本章作了深入阐发,指出经克己复礼工夫实现本体之仁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②故孔颜克己复礼为仁的心法授受实为“十六字心传”的重要补充。朱子道统的根本在于指明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工夫与本体实为朱子道统学不可或缺的两翼。较之“十六字心传”,孔颜“克复心法”具有无可替代之处。它既显示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同时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进路,是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朱子孔颜克复传心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具有意义。
一 “克复心法”与“十六字心传”
我们首先考察孔颜“克复心法”与“十六字心传”内涵之异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分析朱子“心法”一语的含义。朱子“心法”一语显然取自佛学(如唐末高僧黄檗希运作有《传心法要》),现代学者对朱子“传授心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一种更注重“心”与“道”的等同,将“传授心法”理解为传道之法。钱穆先生认为“所谓传授心法,义指较狭,抑且微近于禅家之所谓口传耳授密相付嘱者。……朱子实为不避此传心二字,并始畅阐传道即传心之义”①。另一种着眼于“法”,陈荣捷先生将“心法”理解为“要法”,“传授心法”即指“传授之要道”②,陈氏显然更关注“法”的切要义。朱汉民先生则将“法”理解为“术”,他认为,“所谓‘心法’,亦相当于‘心术’,即一种精神修炼的技艺或方法。”朱氏还区别了“心法”与“心传”的不同意义,认为“心传”与“道统”等同,“心法”与“工夫”“心术”等同,“心法”仅仅具有形而下的法术义,与形而上的“道”存在距离。③我们认为,“法”亦有原则、规律、道的超越意义,它兼具“道”“术”、本体与工夫两面。所谓的“十六字心传”也是指以十六字为核心的传心之法。朱子明确指出,孔颜克复为仁作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并非仅有形而下的工夫义,而是由此工夫通达于形上之仁。在整个《四书集注》中,朱子仅在《中庸章句》解题处与“颜渊问仁”处采用“心法”说,对此“心法”似不应作不同解释。朱子晚年《延和奏札》中亦将“十六字心传”与“克复心法”一并使用,皆称为“前圣相传心法”。再则,朱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作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的“切要”处正在于它更好地将工夫本体、下学上达通贯一体,此正是“克复心法”在道统中不可取代的殊胜之处。
其次,“克复”作为“克己复礼”之简称,在朱子用语中已基本固定下来,达十余次之多,且分布于各种文字。既见于朱子自著,如《四书或问》卷二,“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是以无以致其克复之功”;亦见于朱子与友朋的书信中,如《文集》卷四十四《答方伯谟》,“而从事乎克复之实”,《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而施克复之功也。”既见于与弟子论学记录中,如《语类》卷九十六,“三者也须穷理克复”;亦出于上书皇帝的重要文字,如《晦庵集》卷十一《戊申封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且“克复”之说并非朱子首倡,其前辈杨时即有此说,“颜渊克己复礼,克之己与礼一,而克复之名亡,则圣人之事也。”(《论语精义》卷六)
如上节所述,《中庸章句序》对儒家道统作了最经典之表述,涉及道统人物、传承历程、核心内容等。该序开首即表明《中庸》的使命就是传承儒学精微之道,它对道统的阐发纲举目张、烛幽阐微、透彻详尽。指出道统核心为“十六字心经”,具体又分为两层,尧舜“允执厥中”的四字相传为第一层,显示了道乃“执中”之道,学为中道之学。舜禹传承为第二层,舜禹对尧舜之道有所增益,进一步揭示了如何从工夫实现中道,若仅有一空悬“中道”本体,无实践指点工夫,道统将无法传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之所以授禹也。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该序着力阐发“惟精惟一”的工夫意义,通过“无少间断”的精察理欲,一守本心工夫,来确保“天理之公卒战胜人欲之私”,以达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之中道。
“克复心法”与《章句序》“十六字心传”有诸多相似处,相互映照。从人物谱系看,“十六字心传”是孔、颜、曾、思、孟、程子之传承路线,“克复心法”则代表了孔颜道统授受及程子之庚续。从道统核心来看,二者皆蕴含了工夫主导的思想,“十六字心传”的“精察理欲之间”与“克复心法”的“至明察其几”相对应;“一守本心之正”即仲弓敬恕存养之学,虽不如颜子克复工夫之“至健致其决”,但在最终成就上并无二致。且克己复礼作为工夫纲领之彻上彻下义,完全可以包括“精一”之学。明代朱子学者蔡清即认为“精一执中”工夫为“十六字心传”核心,精一工夫与克复工夫相对应,精察与明察、守正与健决一致。就最终实现目标来看,二者皆追求个体对“天理”本体的体悟。“十六字心传”直指天理胜人欲,道心宰人心,“克复为仁”归于“胜私欲而复于礼,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明代朱子学者蔡清即关联二者论之:
此章言圣贤传授心法。盖从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相传秘指只是一精一执中。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所谓“至明以察其机”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所谓“至健以致其决”也。(《四书蒙引》卷七)卷七
朱子晚年明确指出,两种心法相互照应支持,共同构成儒学道统。在向皇帝进言的两篇重要文字《戊申封事》《延和奏札》中,朱子皆将两种心法一并使用,可证二者实为朱子道统说之代表。《戊申封事》提出,人主之心为天下之大本,人主正心之学,见于大舜精一之传和孔子克复之教。朱子特别指出,精一、克复工夫实现正心之后,仍要归结到一身视听言动之中礼,落实到行事无过不及之执中,如此方能达到天下归仁之效用。朱子意在强调克复、精一应贯穿于心和事,这也表明朱子道统说以修身工夫为主而直达于政统。朱子将舜、孔之说先后对举,显示出舜、孔教法虽异,道之传承却一贯而下的特点。
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①
紧接着朱子以小字形式先后引出对精一之传与克复为仁的注解:
臣谨按:《尚书》舜告禹曰:“人心惟危”……又按《论语》“颜渊问仁”……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辄妄论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
此处虽未以按语形式提出克复心法说,但其意已十分鲜明。朱子在《延和奏札》五中明确提出舜禹精一、孔颜克复之学乃“心法之要”,亦是治本清源之道,进而以此批评士大夫进言皇帝之说,乃舍本求末的做法,批评功利、佛老之说乃为学之偏,君王若受其影响,则将给治理天下带来极大危害。朱子反复强调精一、克复之学作为千圣相传心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全极天理而克尽人欲,本末巨细兼包并举,告诫君王应留意舜禹精一、孔颜克复之学,在言行处事念虑之微中扩充天理,克尽人欲。
昔者舜禹、孔颜之间,盖尝病此而讲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孔子之告颜渊,既曰“克己复礼为仁”……既告之以损益四代之礼乐,而又申之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呜呼!此千圣相传心法之要。其所以极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尽者,可谓兼其本末巨细而举之矣。两汉以来,非无愿治之主,……或随世以就功名……则又不免蔽于老子浮屠之说……盖所谓千圣相传心法之要者,于是不复讲矣。……愿陛下即今日之治效,……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②不仅如此,朱子还有意强调,孔颜“克复为仁”心法较之舜禹“十六字心传”亲切紧要,孔颜授受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其作为道统之特色即在“切要”二字,“切要”体现在克复工夫与仁之本体紧密无间。朱子晚年在《玉山讲义》中特别阐发这一问题,他认为尧舜授受只是说“中、极”,到孔子才创造性地提出仁说,列圣相传之学至此方才说得亲切,此处亦见出孔子贤于尧舜。
珙又请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着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说‘中’说‘极’,今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但至孔门方说‘仁’字,则是列圣相传,到此方渐次说亲切处尔。夫子所以贤于尧舜,于此亦可见其一端也。”①
孔子创造性地对“仁”进行点化提升,使之上升至本体高度,同时又将其落实于人之心性,亲切易感。尧舜所传之“中、极”思想,作为超越性目标虽高明却不平实,与身心性情存在距离,学者不易当身体之。就“克复心法”与“十六字心传”相较而言,前者不仅点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工夫,而且进一步阐发了工夫如何外及于一身之视听言动,贯穿于待人接物之实事中,较之仅言“人心道心”笃实切要,平实可循。故朱子晚年于此章注释益之以程子“发明亲切”的视听言动四箴,以突出“克复”工夫的亲切紧要,要求学者于此更应深刻体悟玩味。“程子之箴,发明亲切,学者尤宜深玩”。在朱子看来,仁与克复乃“地头”与“工夫”关系,工夫与本体合为一体,克复工夫所至当下即是仁之本体,别无间隔。“克去那个,便是这个。盖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复礼’所以为仁也。仁是地头,克己复礼是工夫,所以到那地头底。”②“十六字心传”则工夫与本体明显有隔,此心传历经三代两大阶段的传承才得以完成。尧舜仅以“允执厥中”相传,突出“中”之本体而未告之以“执中”之方。至舜禹授受方才补充“执中”工夫,然仅“惟精惟一”一言,至于如何“精一”并未有说明,在指导学者用功上显然不够紧切。故在朱子看来,“克复心法”实为“十六字心传”之必要补足,元代王柏亦有见于此。他曾引此二封事中“精一”“克复”之学并举为证,指出朱子晚年以“克复为仁”章作为心法切要之言,上接尧舜禹授受的“精一”之学。
王文宪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头。朱子晚年以四箴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传。《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连举以告君而损益四代礼乐,即继于此章之后。”①
二 “心法”之两维:本体与工夫
考察“十六字心传”与“克复心法”,可知本体与工夫为朱子道统说根本问题,二者构成道统之两维,通贯一体,后世黄宗羲所言“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实可代表朱子道统说之精义。尧舜禹“十六字心传”以“中”为本体,“精一”为工夫,先言尧舜本体之“中”,继有舜禹“精一”工夫。“克复心法”则强调“克己复礼”工夫,克复工夫所至,本体之仁自然呈现,二者浑然一体。孔子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仁”本体,使古已有之的“仁”本体化,成为儒学奠基性的主题。而“十六字心传”却以“中”为根本,无法体现孔子对儒学的创造意义,使“夫子贤于尧舜”说流于空虚无力。朱子认为求道工夫虽分殊不拘一格,但却有“切要”与否之别。“十六字心传”偏重“心法”本体一面,虽提出“惟精惟一”之精察、操守工夫,然语焉未详。“克复心法”作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既以“本心之全德”解释了作为本体的仁,更突出了克复工夫之“切要”。
朱子指出孔子言仁虽多,却未曾说出仁体,个人工夫所至,方能见仁之本体。朱子基于工夫论立场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工夫特点作了创造性阐发,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刚健勇决、全面细腻、彻上彻下的“切要”特质,并引入程子四箴说作为对克复工夫之必要发挥,以便学者树立正确为学之方。因着眼工夫平实切用的特点,故朱子特别重视虚实之分,批判程门学者以“理”释“礼”、圣人安仁、万物一体释仁虚空不实,易于导致工夫躐等浮华。基于工夫笃实的考虑,在克己与复礼关系上,朱子发生了从将二者直接等同到认为二者不可等同为一的转变。朱子再三强调,克己复礼工夫的优点在于“亲切”。孔门言仁虽多,最亲切者无过于此,此处言仁与它处之别不在是否言仁之全体,而在于是否亲切。“但‘克己复礼’一句,却尤亲切。”①朱子特别突出了克复工夫刚健勇决的特色,认为此一工夫“非至健不能致其决”,并于“仲弓问仁”章中特别以按语形式,以乾坤二道作为颜、冉工夫之别来强化克复刚健无比的特色。“愚按: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朱子同时还挖掘出“克复”工夫的细腻全面性,提出“克己”指向工夫刚健有为,“复礼”则强调工夫精细全面。克复工夫的精细还体现为工夫之层次性,层层递进,循序而入,由易到难,由粗入精,工夫愈深入愈精微,乃一无穷尽无休止之追求过程。朱子特别强调克复工夫在为仁工夫中的纲要地位,认为它彻上彻下,亦深亦浅,可在最大程度上包容其他工夫。“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②夫子以克己复礼答颜子问仁,是从大纲领言,孔子对其他弟子工夫的指点,皆是从气质病痛处下手,“药病救失”,告之局部“致曲”工夫,最终落实在“克己复礼”这一工夫总纲上。“克复”作为工夫纲要体现为彻上彻下。朱子肯定克复工夫显示了颜子高明于诸弟子处,连仲弓都无法企及,可视为颜子专有,可见克复工夫的彻上性。但朱子越到晚年,则越突出克复工夫的普遍性,强调工夫的彻下。如在戊申年指出即便资质下等之人也得用克复工夫。“今‘克己复礼’一句,近下人亦用得。”③
“心法”应兼顾工夫与本体两面,也是朱子批判佛老、陆氏、浙东功利等学派的理论武器。朱子认为儒学“本末备具,不必它求”,本体工夫通贯一体。朱子由此展开两面作战,一方面既坚持本体的形上超越意义,批评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学派求末丧本,得用忘体。“本是要成物,而不及于成己。”④另一方面,朱子更强调工夫的实践日用义,着力批判张九成、陆九渊“佛学化”的心学,判定佛老与陆学高明空虚,有克己而无复礼,有“一贯”无“忠恕”。指出日用工夫不可间断,由工夫透至本体乃一长期过程,可以言说讨论,心学所主张的不可言说论,违背了圣人的一贯之道。朱子还以散钱和索串为譬,抨击陆氏的顿悟说务为高远而缺乏日用功夫,乃异端曲学,有害于学者,违背了圣人下学上达之道。
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说甚一贯。看他意思,只是拣一个笼侗底说话,将来笼罩,其实理会这个道理不得。……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①
朱、陆道统说之分歧,颇为学界所关注。朱、陆皆认可舜禹“精一”心传为儒家道统主干,但在对待“克己复礼为仁”的态度上,存在重要差异。如前所述,“克复之学”在朱子道统论中居于重要地位,陆氏则提出针对朱子的相反理解。陆氏在给胡季随信中指出克除的对象是“思索讲习”,是“讲学意见”,不仅要克除利欲私念,而且即便成圣成贤这般念头也不可有。“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②朱子发现陆子此说异常兴奋,认为抓住了断定陆氏禅学的有力证据。“因看金溪《与胡季随书》中说颜子克己处,曰:看此两行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分晓。此乃捉着真赃正贼。”③朱子反复以“克己复礼”批判陆氏,他指出意见亦当分好坏是非,不可一概除之。如成圣成贤这般好的正当念头应当有必须有,此正如人的饮食之欲,不可或缺。陆氏“除意见”说既不合圣贤之教,且误导人心,其说如同儿戏,过高而不合圣门之言。“此三字误天下学者!……某谓除去不好底意见则可,若好底意见,须是存留。”④朱子还以“克己复礼”为标准,批判陆氏“心即理”“当下就是”说,指出为学当以克己复礼作为指导工夫,从克去己私处平实下手,不可动辄“当下就是”。陆氏“心即理”说不合下学上达工夫进路,违背了夫子克己复礼之教。心即理乃克去私欲回归天理的本体状态,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而不说心即理,即是担心学者走错为学路径,故教导学者从克复之处真实用功,自可达于圣贤。
三 “克复心法”与求道历程
朱子从理论上建构儒学道统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实践上传承儒家道统。朱子本人时常透露出承担道统之愿望,如《中庸章句序》言对程子中庸之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并谦虚地表示所著《中庸章句》“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其对道统承担之意,跃然纸上。故朱子后学认为朱子乃道统之重要继承发扬者。①我们要讨论的是,朱子所建构的道统说与其自身对道之实践追求存在怎样关系呢?尽管“精一之传”“克复心法”皆为朱子所肯认,但“克复心法”显然具有更为紧切的实践意味。
朱子去世前一年告诫友人,为学只有效仿颜子克复之功,方能做到知行并进,周备无缺,此实为朱子毕生工夫之写照。“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却以颜子为师,庶几足目俱到,无所欠阙。”②朱子一生求仁历程,始终贯穿克复工夫。求学延平时,延平即告以《论语》言仁皆是指点求仁之方,颜子、仲弓求仁工夫尤为得其亲切要领。“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③朱子自此确立了须于日用间克己求仁的为学宗旨。但很长一段时间,上蔡“识仁知仁”说对他影响很大。在经历中和之悟,奠定心性工夫论新规模后,朱子对上蔡观过知仁说进行了反思,于辛卯、壬辰、癸巳年间与张栻、吕祖谦等展开了仁说辩论。首先应提及的是,张栻、吕祖谦在交往中皆提醒朱子应以颜子克己工夫化除气质过于刚直的病痛。如张栻批评朱子平日处事过于豪强,“盖自它人谓为豪气底事,自学者论之只是气禀病痛,元晦所讲要学颜子,却不于此等偏处下自克之功,岂不害事。”①吕祖谦亦言朱子刚直有余、弘大温润不够,当效仿颜子,于自身气质偏处下克己工夫。“以吾丈英伟明峻之资,恐当以颜子工夫为样辙。”②在仁说辩论过程中,朱子更为重视仁的名义剖析,张、吕则反复提醒他克己工夫的重要,朱子诚恳接受之。朱子晚年也曾反思自身气质偏于忿懥。
朱子曾撰写《克己斋铭》以为自警。理学前辈多有以“克己”为斋名、铭文者,朱子唯独对程子克己四箴说推崇备至,病危临殁之时,仍请杨子直为其书写四箴用以自我提撕警醒,祛除病痛。朱子坦言对程子“四箴”的认识有一个“见其平常”到“觉其精密”的转变。此皆可证克己复礼实乃朱子一生修身工夫之指针。
欲烦为作小楷《四箴》百十字。……此箴旧见只是平常说话,近乃觉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坠云耳。……欲得妙札,时以寓目。③
去世前十二天(该书有注:此庚申闰二月二十七日书,去梦奠十二日),朱子处于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去信催问四箴之札,真正实践了生命不息,克复不止的工夫追求,此朱子所以堪为万世师表之所在也。“前书所求妙札,曾为落笔否?便中早得寄示为幸。”
从朱子对自身写照、反思文字来看,其为学追求亦是通过克复工夫以达到仁礼合一境界,特别重视通过遵守外在之礼以彰显内在之仁。《书画像自警赞》自述以礼法和仁义为用力目标,此目标正落实于克复工夫之中。“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癸巳年四十四岁所作《写照铭》称“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其工夫还是以程子四箴“制外以养其中”的克复为主旨,言“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朱子对弟子之教非常注意礼之实践,如讲解诚意章时批评陈文蔚袖角有偏。他本人晚年最大写作计划是编纂《仪礼通解》。黄榦所作《朱子行状》细致描述了朱子于视听言动诸举止上严格遵守诸礼之表现,“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特别突出了朱子临终前对礼法的恪守不渝,此足显出朱子一生求道工夫端在克己复礼也。“先生疾且革,……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蔡沉《朱文公梦奠记》所载与此不同,更强调了朱子克己复礼之精神。“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沉正之。”
四“克复心法”说的道统意义
据上述可知,“克己复礼为仁”不仅被朱子视为心法,而且是“切要”之法。“十六字心传”通过对道统历史渊源的追溯,增强儒学道统说之神秘性与历史性,以寻求更大认同,但同时也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在《中庸章句序》中,以“十六字心传”为内容的道统被分为两个有差别的阶段:尧、舜、禹、汤、文、武圣圣相承,大道得行、内圣外王一体时代,以政统为核心;自孔子后,进入德与位,道与政相脱离时期,儒学转向了道统和学统的合一,以学统为核心。通读《章句序》全文,不难感受到,第一阶段的道统说居于中心地位,其开创性意义远远超过此后以孔子为代表之道统传承阶段,《章句序》重心皆在前两段文字中,彰显了三代君主对于道统的开创之功,孔子对道统相传之功显然相对矮化了。为此,朱子不得不刻意强调,“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但此处在道统的意义上,显然无法体现孔子“继往开来”之功要贤于尧舜开创道统之功。朱子有心推崇孔子,但实际上却不得不突出尧舜,无形中削弱了孔子,这就是朱子所面对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之贡献不在于对“中”之继承,而在于仁之创造性提升,为人的精神世界树立了大本大原。故孔子即便贤于尧舜之功,亦不可在以“中”为核心的道统上与尧舜相较。
朱子对此困境有明确认识,这从他对“中”的诠释修改中皆可看出。朱子认为“中”有两层含义:尧舜提出的无过不及的已发之中和子思提出的不偏不倚的未发之中。孔子只是继承了尧舜的已发之中说,《集注》把“尧曰”章“允执其中”的“中”注为“无过不及”即透露此点。朱子弟子辅广指出,《集注》曾经以“不偏不倚”释此“中”,后删改为“无过不及”。盖此处并非指未发之中,未发之中乃是子思首倡之,孔子此处仍是继承尧舜之说,言事上已发之中。“辅氏曰:《集注》初本并‘不偏不倚’言中,后去之而专言‘无过不及’者,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至子思而始著于书,而程子因以发中一名而含二义之说。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注》只以无过不及言中。”①元代胡炳文亦持子思发明未发之中说,“自尧舜以至夫子,所谓中者,只说‘已发之中’,而子思独提起‘未发之中’言之。……大哉斯言,真足以发千古之秘矣。”胡氏认为从尧舜到孔子谈到的“中”只是已发之中,到子思才提起未发之中说,子思的贡献在于提出未发之中,把握了中的本体义,揭发了圣学的千古奥秘所在。但此观点显然更削弱了夫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夫子对道统核心之“中”有何贡献可言?其道统地位如何能彰显呢?这的确是很值得玩味的。
朱子“十六字心传”道统说既未能彰显孔子崇高处,又导致颜回在道统中的失落,自然引发后世学者不满。但朱子从孔颜“克复为仁”之授受找到了突破点,突出了孔颜在道统上的崇高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朱子“此亦见孔子贤于尧舜”说才具有说服力。可见朱子“克复心法”说在儒家道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站在后人的立场,朱子“克复”心法之说的道统意义,尤为重要。
从历史客观性而言,孔颜授受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十六字心传”因奠基于并无确切史料根据的传说中,清儒通过证伪“十六字心传”,对此说进行了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攻击,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道统说。不管后来学者如何为“十六字心传”辩护,指出甚至撇开文献真伪,该说自有其思想意义,但如此重大思想建立于虚假材料基础上,总是大大影响了其理论说服力。如有学者已指出阎若璩“十六字心传”辨伪给理学带来的巨大冲击意义,“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还剥夺了程朱理学的经典依据,对一向以尧舜三代万世心法继承者自视的程朱理学,不啻釜底抽薪之击。”①为此,学者有意在《论语》、《尚书》关于“中”的论述外,找出《周易》有关“中”的论述,以完善儒家道统的“时中”说,印证“十六字心传”的可靠性。②而孔颜授受之儒学道统说,则将道统说奠基于极为坚实的基础上,改变了此不利局面。
此说凸显了孔子对于儒家道统的创造意义。孔子对仁的创造性提升与开拓,奠定了儒学发展的基调。他对仁的最重要阐发,即见于克己复礼为仁之说。正如朱子所认为的那样,此处方才见证了孔子贤于尧舜处,方显出孔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盖在尧舜禹所传“十六字心传”之道统中,孔子仅仅居于传承者地位,未显出其对儒学之特殊贡献。“克复心法”则充分展现了孔子以仁学对儒家道统之开创,是道统之作者而非述者。此说与后世学者不满足于仅以“述经”事业者看待孔子,推崇孔子开创之功的思想一致,古人如胡五峰、今人熊十力、牟宗三等即力推孔子仁说对道统开创之功。
“克复心法”之传以孔颜授受为标志,具有极为广阔的包容性,能最大程度容纳儒学内部各家之说,易为各家所共同接受。孔颜在儒学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威望,孔颜授受较之孔曾、孔孟等传承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能得到理学、心学、功利学派等各家之认同。儒学各派基于不同立场,对曾子、孟子学不尽表认可,但对颜子之学一致称赞而绝少异议。“学颜子之所学”为各家所共许之入道之门。史上有学者对颜渊在孔门道统中地位之被忽视甚表不满,特补充之。如明代丰坊伪造的《石经大学》在“正心”章补入“颜渊问仁”二十二字,李纪祥先生认为,“丰坊特意提出颜渊,旨在针对朱子所建立的孔、曾、思、孟道统而反对之。”③陈逢源先生亦认为丰氏此举意在“补充朱熹建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统之传中失落的环节。”此论似未注意朱子倡导“克复心法”以树立颜渊在道统中卓越地位的苦心。
近来有学者对阳明学派推崇颜子学贬低曾子学有细致论述,认为阳明学派力图通过崇颜贬曾,突出孔颜道统之传,自认接续颜子的方式来夺取程朱道统思想的话语权。①这个论断很有意思。一方面,程朱学派对颜子非常推崇,仅将颜子置于孔子一人之下。程子大力提倡“学颜子之所学”,朱子对颜子的成就有总结性论述,提出了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在“崇颜学颜”这一旗帜上程朱、阳明学派并无差别,当然在对颜子内涵的解读上,二者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两家的根本差别在于阳明学派对曾子的贬低,“贬曾”其实并非阳明学派的创见,早在宋代,陆象山、叶水心就表达了对曾子的贬低。当然,程朱学派是颜、曾一并推崇,在他们看来,即便颜曾有高下之别,也是互补而绝非对立,尤其对于学习者(教法)来说,曾子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颜子。心学一派刻意突出颜、曾的差异,自然有其思想根源,但事实表明,尽管刻意渲染颜曾的对立,阳明学派并未实现对程朱道统话语的颠覆。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看,颜、曾子并列说更为学术界所接受。
孔颜仁学授受,表明儒学道统以内圣修为之学统为根本,并不有赖于政统与治统。②而尧舜禹之“十六字心传”,含有很大的政统成分。儒家特质在心性内圣之学,理解这一点对划清儒学在未来发展中与政治之纠葛,从而在政教分离的现实社会中更好推动儒学向前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就此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许多问题,诸如新儒家所建构的内圣开出外王说是否必要?“政治儒学”是否是儒学的发展方向?生命之体证、礼乐之教化是不是对于儒学具有更紧切的意义等。
“克复心法”乃工夫与本体之结合,尤为强调工夫的意义,彰显了儒家之学以实践工夫为主的特质。这一点在朱子的孔门弟子之评中亦得到体现。如朱子认为子贡与曾子境界之别体现在知、行上,二子皆闻夫子一贯之道,“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子贡博闻强识,由知入道;曾子与之相反,于践履笃实上下工夫,由行入道。曾子实处用工,更为可行,领悟更加透彻,子贡知上工夫过多,行上不足,故对道之领悟不如曾子。朱子引尹氏说指出,“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论语集注·卫灵公》)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无工夫即无儒学,即无道统。朱子正是从工夫角度指出此心法授受更为亲切紧要,它关涉为学工夫的各个方面,彻上彻下,内外并包,不同资质者皆可循此用工以达于圣域。这点明了未来儒学之开拓发展,必须以实践工夫为支撑,否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克复心法”以工夫为本,它与以阐发本体为主的《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正好相互补充,相得愈彰。
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诠释花费了巨大心血,于晚年最终将其提升到“心法切要”的地步,作为“十六字心传”的补充与深化,体现了朱子的睿智。元代朱公迁亦认为圣贤对道统的表述存在差异,或正面表述所得道统,或间接表述道统所在,或直接承担道统,或谦虚不敢承担。孔颜克复之功,孔曾一贯之旨即正面直接表述何为道统,“愚谓圣贤或正言以叙道统之所得,或因言而见道统之所在,或直以为任,或谦不敢当,语不无少异也。其在孔门则克己复礼之功,吾道一贯之旨意乃其正言者。”①孔颜“克复心法”突出了孔颜授受在儒学道统史上不可取代的独特意义,同时发展了程颐所倡导的“学颜子之所学”的理学主题。它表明整个儒学道统的延续,皆须以孔颜之学为准的,以下学上达的工夫本体为根本路向。以现代眼光来看,“克复心法”这一以孔颜授受为标志的道统线索对儒家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工夫与本体这一主题对于儒学发展的根源性意义,指明了未来儒学之发展,应继续循此方向推扩。
第三节 孔曾忠恕一贯之传
在整部《论语》中,朱子特别重视“忠恕一贯”章,认为忠恕一贯乃儒学第一义,本章是《论语》最重要一章,对此章理解关涉到对整部《论语》的认识,亦反映出个人儒学造诣的高低。“问‘一以贯之’。曰:‘且要沉潜理会,此是《论语》中第一章。’”①朱子提出忠恕一贯章于孔门居第一义的原因在于它是孔子晚年亲传宗旨,对其他说法具有纲领性的统领意义,它道出了儒学之本体、功夫与境界,与佛老视空虚为本体、顿悟为功夫者根本不同。此宗旨自秦汉以来只有二程兄弟才接续之,二程门人亦只有谢上蔡和侯师圣于此有得。“‘一以贯之’乃圣门末后亲传密旨,其所以提纲挈领,统宗会元,盖有不可容言之妙。当时曾子黙契其意,故因门人之问,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来。则其一本万殊,脉络流通之实,益可见矣。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皆不能晓,直至二程先生始发明之。而其门人又独谢氏、侯氏为得其说。”②故朱子花费一生心血,从道之体用出发,以理一分殊注释“忠恕一贯”,阐发儒学体用思想,以此展开对其他思想的批判,在朱子经典诠释和《论语》诠释史上皆具重要意义。
一 忠一恕贯
朱子对“忠恕”章的注释以二程之说为基础,将自身看法揉入其中,阐发了忠恕体用一贯义。本章原文仅有35字,注文则多达500字,足为原文十数倍。原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③
“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朱子首先从圣人境界讲“一以贯之”,阐发“一以贯之”所体现的理事体用义。“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里仁》)圣人全体是理,作用出来即是理之显现。虽然呈现出的作用各不相同,然皆贯穿着同一之理,是同一下的差别,分殊中的普遍。当同一之理作用于具体事物时,就表现出一种自然差异,即理一分殊也。这个理是指天地万物共具的普遍同一之理,和它相对的则是具体特殊的事物。曾子通过持久不懈的日用工夫,达到了对具体事物分殊之理的理解,经过夫子点醒,最终了悟天地共具之理,才以“一以贯之”说表达之。①当然,朱子对理一分殊的认识主要还是从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角度着眼,以之解决以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故朱子在此将一贯之本体始终放在心上讲,突出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的关系,提出圣人心与理一,心尽万理,物我无间。
朱子新解在于将理本体与《中庸》诚本体相沟通,把圣人浑然一理与天地至诚无息说结合。天地有诚而万物得所,圣人显理而万事得当,道体具有真实自然,创生不已的特质,是天地殊异万物皆具之同理;万物各归其位,各尽其性,则是道体自然发用。据此凸显圣人一以贯之的真实存在,因为圣人在至诚意义上与天地相沟通,故能如天地本体对万物造化一般,历历可见,无处不在。“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论语集注·里仁》)朱子以一本万殊解释一以贯之,以诚为万物之本,万物为诚之用,和《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对应,皆是言理事体用的一多关系。“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论语集注·里仁》)弟子担心体用之说有分成两物之嫌,朱子认为体用一物,不可分离,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二者浑然一体。朱子还强调对于此理本体,不须多说,因为本体不可见,不可言,多说反而失其本意。“要之,‘至诚无息’一句,已自剩了。”②
忠体恕用。朱子采用程颐“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说来定义忠恕,忠即是尽己,恕即是推己。忠恕就是以己为中心对待己和他人的两种方式。忠和恕皆是从心上言,尽己和推己之己皆是指己之心。朱子对“尽己之心”的“尽”提出极高要求,认为当百分之百穷尽己心,不能有丝毫姑息和欠缺,否则就不是忠。“尽时须是十分尽得,方是尽。若七分尽得,三分未尽,也不是忠。”③至于如何尽己,就不仅是理论问题,而应当在日用事为上体验、印证,否则空说无益,反致偏离本义。朱子还从语言学角度,根据字形特点,采取《周礼疏》对忠恕的解释:“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此解更为突出了忠恕在心上的意味。朱子认为忠就是真实,“忠只是一个真实。”心中所具之理必须真实,否则无法发用出来,唯有真实,其发用才无不得当,轻重厚薄大小一一合宜,这同于《中庸》不诚无物说。批评“尽物之谓恕”说,因为恕之得名,只是推己,恕只是从尽己之忠流出,流而未尽也,“‘恕’字上着‘尽’字不得。”①
朱子引用大程子说,以仁、恕对言解忠、恕,仁指人己物我之间没有间隔,无需推扩,自然及物;恕则需要一个推己及物的过程,二者之别仅在于自然与勉强。“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朱子指出程子说仁合忠恕之义,体用兼具。若直接以仁解一贯,反失其用意,无以见体用之分。“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将仁解一贯字,却失了体用,不得谓之一贯尔。”②在圣人分上,忠和恕相当于诚和仁,但诚、仁之间关系相隔太远,无法彼此切合;且诚、仁皆偏于本体义,未见体用相别义,忠恕则关系紧密,即本体即发用,故不可将忠恕换为诚和仁。“‘忠’字在圣人是诚,‘恕’字在圣人是仁。但说诚与仁,则说开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连续,少一个不得。”③“然曰忠曰恕,则见体用相因之意;曰诚曰仁,则皆该贯全体之谓,而无以见夫体用之分矣。”④
朱子指出忠恕正当之义乃日用为学功夫,此处借言阐发形上普遍之理,因为一贯之理无形而难言,故借学者忠恕工夫以显言之,其实是为了使学者更好理解道。“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引程子说以天道解忠、人道解恕,“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这个天人之别凸显了自然一体和人为发用之别,乃本体和发用关系,二者并无高下层次之分,“忠是自然,恕随事应接,略假人为,所以有天人之辨。”⑤它和《中庸》中“天之道、人之道”不同,《中庸》所指是本体和工夫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跃进、提升过程。
忠、恕是大本与达道的体用关系。“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忠者,尽己之心,真诚不虚,实而不假,故为道体;恕者,乃是忠之发用流行,必由此心推扩而出,方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谓道之用。“大本达道”见于《中庸》中、和的体用关系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但它与《中庸》忠恕说不同,“忠恕违道不远”乃是日用工夫义,此处忠恕是高一等说,是把忠恕本有工夫义转换成本体作用义,指本体之自然发用。“‘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①朱子强调忠恕的体用合一,不可相离,好比形影关系,有其一必有其二,本体之一即在发用之多中。“忠、恕只是体、用,便是一个物事;犹形影,要除一个除不得。……忠与恕不可相离一步。”②正因为忠恕是体用本末关系,故忠对恕具有主宰决定作用,“无忠则无恕,盖本末、体用也。”③朱子采用诸多比喻来突出忠恕的这种关系,如将忠、恕比作本根和枝叶,这可说是一种本原和派生关系,“忠是本根,恕是枝叶。”还将二者喻成印板和书的关系,表明二者乃普遍之理和分殊之理关系。朱子引小程子说,从天命不已,各正性命的角度入手,以天命不已言忠,各正性命言恕,天命不已即至诚无息,于圣人分上,此忠自是至诚不已。“‘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至于变化性命,朱子指出这正是言理一和分殊处,圣人之于天下,正如天地之于万物,皆是一心而遍注一切,物物皆具一理,人人皆有圣人之心,此心此理自然遍在,这便是圣人忠恕。“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圣人之心自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圣人之忠恕也。”④
朱子从心与事的区别来看待忠恕关系,忠在心上,恕则在事,心具众理,一心应对万事,万事皆从心发。“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①朱子还以心、事说区别不同的忠,指出心上之忠是本体,事上之忠则是工夫,前者是统体义,后者仅是具体事上义,这即是曾子忠恕之忠和谋而不忠之忠的区分,“‘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为人谋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统体;主事言者,主于事而已。”②朱子对忠信和忠恕说作了比较,指出信、恕之间存在差别,突出恕的过程含义,乃是作为本体“忠”之发用,信虽然也是忠之发用,但显示的是发用之结果,为一具体定在。以树为例,恕好比气对枝叶的贯注过程,信好比枝叶对气的接受;恕好比是行,信则好比到了目的地。“枝叶不是恕。生气流注贯枝叶底是恕。信是枝叶受生气底,恕是夹界半路来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头说。发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无忠,便无信了。”③
忠一恕贯。朱子指出忠恕即是一贯之实,一贯由忠恕得以透显,一是忠,贯是恕,忠贯恕,恕贯万事。“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贯之底注脚。”④忠、恕分别为一和贯,除此之外再无独立的一贯。“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忠恕的一理、分殊关系,是作为本体的抽象超越的普遍之理与在个别事物、日用行为中所体现出的分理关系,二者在性质上相同。一理万殊,体一用殊,皆是说明本体必须通过现实多样的作用显示出来,在表现形态上多种多样,但在理上则是同一。恕上各分殊之理即是从忠上同一本体之理所发出。“忠即是实理,忠则一理,恕则万殊。”⑤“忠恕一贯,忠在一上,恕则贯乎万物之间。只是一个一,分着便各有一个一。……恕则自忠而出,所以贯之者也。”⑥
朱子强调事上践履工夫于领悟一贯本体之重要。认为理会分殊之理是领悟理一之前提,不经过恕上分殊则不可能实现忠之理一。曾子能承当孔子点醒,悟出一贯之理,正因为曾子此前已经在事上一一理会践行过,在日用礼教诸多方面下了诸多学习之功,于分殊上尽皆知了,只是对本体尚无了悟,故闻“一贯”之语而当下有悟。其他弟子未曾下如此工夫学习,不可承当此语。而且即使没有孔子当下之点醒,曾子本人工夫所至,终能契悟。在为学功夫上,朱子反对摒弃外物而仅仅专意于内心的守约之学,突出曾子于礼上事上的探究工夫。“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论语集注·里仁》)“却是曾子件件曾做来,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践履,如何识得。”①朱子还从为学先后次序出发,指出曾子讲出理一之说已过于分明。“曾子是以言下有得,发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②
朱子喜用散钱、木片设喻,告诫弟子应象曾子那样在分殊上学习,在用上一一做工夫,本体自然有得;反之,仅空谈本体而无下手工夫,则无法真正达道。“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今人钱也不识是甚么钱,有几个孔。”③它所造成的流弊使天资高者流于空虚之佛老,低者则糊里糊涂,为自造之网所遮蔽,反倒丧失儒家重实用之义。“不愁不理会得‘一’,只愁不理会得‘贯’。理会‘贯’不得便言‘一’时,天资高者流为佛老,低者只成一团鹘突物事在这里。”④朱子极为反对工夫上的精粗说,认为理无精粗,正如水一般,田中、池中、海中水只有量的多少之别,并无质之不同,以此证明分理和一理是相同的,故在为学工夫上并无精粗之别。“圣人所以发用流行处,皆此一理,岂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⑤
二 “一以贯之”
除曾子外,孔子亦告子贡“一以贯之”之理,“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集注·卫灵公》)朱子对此亦进行了深入阐释,指出此章主旨和“忠恕一贯”章相同,乃孔子点醒子贡儒家一贯之理,告之当从工夫上达本体,强调本体工夫的一体。此章诠释,朱子尤为注重和“忠恕一贯”的比较。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突出为学工夫的重要,朱子视积学工夫为达到一贯之理的必要前提。孔子之所以告诉子贡以一贯之理,因为子贡学问工夫已接近证悟本体,故夫子当其可而告之。朱子批评学者对此章理解不顾积学功夫而空谈一贯之理,并再次以钱和钱索为喻,证明分殊和理一不可偏废关系。
二是应将博学多识和一以贯之结合起来。在肯定博学功夫必不可少的同时,朱子指出圣人为圣,并不仅在于此,更在于体悟本体之理,贯穿于博学工夫中。今人徒有博学而未至于圣者,即在于未悟一贯之理。“今人有博学多识而不能至于圣者,只是无‘一以贯之’。然只是‘一以贯之’,而不博学多识,则又无物可贯。”①
三是较之“忠恕一贯”章,朱子对此章诠释更侧重阐发本体。此处《集注》引谢氏说突出本体自然流通贯注义和高远神妙义,认为对此本体只能意味涵养,不可言说用力。“谢氏曰:圣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观而尽识,宜其以为多学而识之也。然圣人岂务博者哉?如天之于众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贯之。’‘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论语集注·卫灵公》)朱子曾和方宾王讨论一以贯之章,方宾王以体用本末,万殊一本,一体万有之说解此,指出子贡通过致知工夫已体悟天理所在,只是未能悟出理一之妙,夫子因此点化之,证出为学之工夫于体悟天理中实不可少,朱子认同其说。
四是突出曾子、子贡入道之异和境界高低,子贡由知而入,曾子由行而入,“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论语集注·卫灵公》)在入道境界上,子贡与曾子皆闻夫子一贯之说,子贡由知上下工夫,博闻强识,由知入道;曾子恰与之相反,于践履笃实上下工夫,由行而入道。曾子从实处下手,工夫更为可行,领悟更加透彻,子贡却似乎在知上工夫过多,对道之领悟不如曾子。“尹氏曰:‘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论语集注·卫灵公》)顺此,朱子分析了颜子、曾点、子贡、曾子四人的工夫境界。颜子天资悟性高,在事上工夫极深,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子贡天资虽高,却偏于知上,日用工夫粗疏不足;曾子天资低,然而靠着刻苦工夫,于事上逐一做透,最终获得对道体领悟。曾点仅仅是知上见到理一,事上却无工夫。朱子认为一定要在具体实事上,在“贯”上实下工夫而不是凭空想象本体“一”,事上工夫到了,自然能够领会理上之一;反之,次序颠倒矣。批评仅仅想象个万殊一本重知不重行的情况,同时也批评只在分殊上做得好,却没有体验到一贯本体者,指出圣人之教,须从具体事情上知行并进,体用结合,缺一不可。“颜子聪明,事事了了。子贡聪明,工夫粗,故有阙处。曾子鲁,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来推去,事事晓得。”①
三 忠恕说的意义
三层含义。朱子认为忠恕经过层累诠释,被赋予了三层含义,第一层是程子所说天地无心之忠恕;第二层是曾子所说圣人有心无为之忠恕;第三层是《中庸》所言学者日用工夫进路之忠恕,其中学者日用工夫义之忠恕才是其本义所在。“天地是无心底忠恕,圣人是无为底忠恕,学者是求做底忠恕。”②“论著忠恕名义,自合依子思‘忠恕违道不远’是也。”③在孔子那里,其实只是说出了一贯这个本体而已,忠恕则是曾子所推出,以体用说忠恕亦是后人所言。“夫子说一贯时,未有忠恕,及曾子说忠恕时,未有体用,是后人推出来。”①忠恕的三层不同含义归结起来又只是一个忠恕而已,只是等级有差别。“皆只是这一个。学者是这个忠恕,圣人亦只是这个忠恕,天地亦只是这个忠恕。”②“其实只一个忠恕,须自看教有许多等级分明。”③朱子认为圣人全体是理,与天合一,不过天浑然一本,圣人则与物相接。圣人本体与工夫早已浑然一体,无须“尽”和“推”之工夫,故圣人头上本无忠恕,忠恕只是对学者做工夫而言。“圣人分上著忠恕字不得。”④“天地何尝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与恕。故圣人无忠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学者之事。”⑤然而,朱子同时又坚持认为,圣人亦离不开忠恕,它和学者之别在于工夫极为自然超脱,自然流出,无须推扩,学者则勉强生硬,但其最终所指向目标则是一致的。“圣人是自然底忠恕,学者是使然底忠恕。”⑥
现实批判。朱子以理一分殊说诠释忠恕一贯,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朱子以之两面作战,一方面既坚持忠恕说的形上超越意义,批评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学派求末丧本,得用忘体;同时又强调忠恕的日用工夫义,对心学的佛学化提出批评,对张九成、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及佛学进行批判,要求学者须实下功夫,本末一致。
朱子认为一贯本体须经由日用博学工夫积累而至,批评那种仅限于具体知识的掌握而不探求大本的做法,将工夫花在事为之末而没有抓住大体根本,故无法体认一贯之形上超越义。在他看来,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即有此弊,偏于博学多识而无一贯之本,未能做到下学上达的本末一体。“近见永嘉有一两相识,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那个都未有用处,却都不济事。吕伯恭向来教人亦云:‘《论语》皆虚言,不如论实事。’便要去考史。”⑦
朱子更主要的批判对象是以张九成、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及佛学思想。他批评张子韶的合人己为一贯说,认为根本不涉及人己关系,而是言工夫本体。“‘吾道一以贯之’,今人都祖张无垢说,合人己为一贯。这自是圣人说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己说得!”①他极力反对心学的顿悟本体说,指出日用工夫不可间断,不存在突然觉悟,顿觉前后皆非之事。因为由工夫透至本体存在一长期过程,可以言说讨论,心学则认为不可言说,违背了圣人的一贯之道。“今有一种学者,爱说某自某月某日有一个悟处后,便觉不同。及问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说。便是曾子传夫子一贯之道,也须可说,也须有个来历,因做甚么工夫,闻甚么说话,方能如此。”②朱子还是以散钱和索串为譬,抨击陆氏学的顿悟说务为高远而缺乏日用功夫,乃异端曲学,有害于学者,违背了圣人下学上达忠恕一贯之道。“江西学者偏要说甚自得,说甚一贯。看他意思,只是拣一个笼侗底说话,将来笼罩,其实理会这个道理不得。……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③
朱子批评学者与曾子差别在于工夫上的“虚”与“实”,学者“只得许多名字,其实不晓”,曾子是实下工夫,以真诚之心践道,对一贯之道有真实体验。“如今谁不解说‘一以贯之’!但不及曾子者,盖曾子是个实底‘一以贯之’;如今人说者,只是个虚底‘一以贯之’耳。”④学者之弊在于只是空自想象比划出一个大概意思,空知一二而无真实工夫;或徒知在事上用功而未能窥探本体。“而今学者只是想象得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实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细微紧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见得那大本。”⑤
在诠释方法上,朱子强调应注意分析、落实概念的具体含义,注意其本义与言外义,以及和其他概念的同异关系。批评浙东学派对忠恕的理解牵强附会,笼统不分,含糊不清:“今日浙中之学,正坐此弊,多强将名义比类牵合而说。要之,学者须是将许多名义如忠恕、仁义、孝弟之类,各分析区处,如经纬相似,使一一有个着落。”①批评学者将忠恕理解为不自私、不责人说在现实生活、日用工夫上皆行不通,违背了儒学宗旨。“问:“或云,忠恕只是无私己,不责人。”曰:“此说可怪。自有六经以来,不曾说不责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已,何尝说不责人!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②
四 忠恕说的形成及特点
(一)朱子对忠恕一贯的理解是一个长期的自我扬弃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几个阶段:从学延平期、初步形成期、晚年修改完善期。
从学延平时朱子就奠定了对忠恕一贯的基本看法。正是通过探究忠恕一贯,朱子才逐步厘清了儒释两家在本体与工夫上之差别,从释老之说中走出,归本伊洛之学。此时,朱子与延平、范直阁等人广泛深入的讨论忠恕说,他采用理一分殊来解释忠恕和一贯,提出二者是工夫与本体关系,当于忠恕工夫透悟一贯本体,一贯本体即在忠恕工夫中,二者不即不离。道体无处不在,曾子忠恕说乃是因门人之问道出自身对道体契悟,并指出忠恕于圣人和学者各有不同意义。“忠恕两字在圣人有圣人之用,在学者有学者之用”。圣人分上全体是一,即工夫即本体,工夫本体浑然合一,达到了体用不分,当下即是之境界,故本无须言忠恕。学者未能打通下学上达、工夫本体界限,故忠恕工夫乃是对学者而言,为学者入道之必要进路。但圣凡之别仅仅在于对本体彻悟不同,在于工夫自然纯熟不同,其进路与所至则同。下学至于上达后,自然消除了圣凡之间的界限。
因为此前虽然已“略窥大义”,然“涵泳未久,说词未莹”,故朱子还专门写有《忠恕说》。朱子《忠恕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用理一分殊阐发忠恕一贯,突出下学和上达的工夫本体关系。工夫久之自将上达本体,而彻悟本体后,平常日用将贯注本体光辉,赋予超越意义。二是人在处理世界时,最主要的是合宜处理己与物的关系,此即忠恕之道。由忠恕工夫可上达本体,而知人己物我为一。朱子特地引用二程对忠恕的定义式解释,“自其尽已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三是提出忠恕体用关系,反对脱离日用忠恕工夫而空谈一贯本体。朱子曾将此说呈给延平,延平基本认同。朱子晚年回忆此说,大体仍表满意,他认为与范直阁讨论‘忠恕’,虽然“此是三十岁以前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①朱子批评吴耕老将忠恕和一贯割裂的看法,提出忠恕即在一贯中,本体不离工夫,即工夫以显本体。
延平逝世后,朱子通过对二程及其弟子著作的研读整理,通过与湖湘学派的交流,对忠恕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一是他认为忠恕即道之全体,忠即是体,恕即是用,二者合起来体用兼具,这样来看“一贯”,方有着落,特别强调恕乃是从忠发出,不是从“一贯”流出。二是继续强调忠恕两个层面的区分,一个作为学者“入道之门、求仁之方”;一个反映圣人道体本然,忠、恕、诚、仁皆相通无隔。朱子忠恕解受程颢、谢良佐的影响极大。“示谕忠恕之说甚详,旧说似是如此。近因详看明道、上蔡诸公之说,却觉旧有病,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忠体而恕用,然后一贯之语方有落处。若言恕乃一贯发出,又却差了此意。如未深晓,且以明道、上蔡之语思之。”②此后,朱子一直坚持忠恕的体用义,提出忠实然不变而创生不已,恕则遍布天地,显露无碍,二者虽然特点各异,然却体用一源而不可析离。“近看得忠恕只是体用,其体则纯亦不已,其用则塞乎天地;其体则实然不易,其用则扩然大通。然体用一源而不可析也。”③
朱子晚年还在修改完善忠恕说。如壬子年(1192年)与郑子上讨论修改这一章,郑子上提出,今本删去前注中的“此借学者而言”将会造成下文语义不明,朱子告之并没有删去对忠恕说明的“忠也,恕也”,忠恕本来就是学者分上事。按:今本亦保留了“借学者而言”之义,改为“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朱子还提出已经把此前“道体无二而圣人”改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这样语义就很清楚了。按:这和今本“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还是有所不同。在去世前五年的乙卯(1195年),朱子又修改了忠恕说。他告诉曾无疑忠恕本来即是学者事,与圣人其实无关,不必顾虑说得过高,忠恕可以从深浅两个层面来理解:浅言之,即日用常行之道,愚夫愚妇皆须由之,乃人立身根本处。深言之,即使圣人神通广妙,也离此忠恕不得。朱子强调忠恕虽在日用常行之中,但应有对本体之彻悟,于理上见得分明,方能赋予忠恕超越的一面。否则,仅仅限于一言一行之忠恕,未能由日用工夫把握忠恕之深层本体,将陷于拘执无用的死忠恕,只能成就个常人。“孝悌忠恕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①
朱子曾自述参究忠恕说的经过,特别提到二程的启发之功。他认为此问题关涉到对儒家本体与工夫之认识,自己能理解此章,在于将明道解释忠恕说的两段分散之语放到一起,由此悟出忠恕于学者的工夫义和圣人的本体义。否则,两重含义纠缠一起,将无法理解。朱子为此还和认同龟山之说的学者进行争论,“旧时《语录》元自分而为两,自‘以己及物’至‘违道不远是也’为一段,自‘吾道一以贯之’为一段。若只据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后云‘此与违道不远异者,动以天尔’,自说得分明,正与‘违道不远是也’相应。”②“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为两段。后在籍溪家见,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义极完备。”③
朱子同样十分感激二程门人谢氏、侯氏说给予他的帮助启发,指出忠恕说“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
惟侯氏、谢氏晓得。”①事实上,谢、侯对此章说法甚多,不少地方都遭到朱子批评,但是在关键处予朱子莫大启发,故朱子于二人之说始终深为感激。谢、侯说哪些地方予朱子以启发呢?朱子满意于谢氏从理一分殊角度阐发忠恕说。“谢氏曰:忠恕之论,不难以训诂解,特恐学者愈不识也。且当以天地之理观之,忠譬则流而不息,恕譬则万物散殊,知此,则可以知一贯之理也。……又问忠恕之别。曰: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恕,如心而已。”②故他称赞谢氏对忠恕的理解最好,其次侯氏说和刘质夫的记录也对他颇有助益。二程其他弟子如龟山、尹氏等纠缠于《中庸》忠恕说和此处之说,而未能看穿二者含义差别。“此语是刘质夫所记,无一字错,可见质夫之学。其他诸先生如杨、尹拘于《中庸》之说,也自看明道说不曾破。谢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见未尽处。”③
(二)据上述可知,朱子主要是继承二程思想,以理一分殊之说解释忠恕一贯,认为忠恕即是一贯,朱子的这一诠解在整个《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对这一章理解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理解忠恕与道的关系。忠恕的本义是尽己推己之为学工夫,是达到道的途径,它与道是有距离的。这一点在《中庸》中有明确的说法,“忠恕违道不远”。正因如此,学者在理解曾子此说时,多受制于《中庸》说,不敢明言忠恕即是一贯之道,其中包括二程亲传弟子。朱子的突破在于接续二程说,肯定此处忠恕表达的是本体义,是一种借言,是“升一等说”,突破了《论语》、《中庸》文本之间的矛盾。他在《中庸或问》的“道不远人”章对此有具体说明,“诸家说《论语》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贯之’之义;说此章者,又引《论语》以释‘违道不远’之意,一矛一盾,终不相谋,而牵合不置,学者盖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谓‘动以天者’,然后知二者之为忠恕,其迹虽同,而所以为忠恕者,其心实异。……曾子之言,盖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学者默识于言意之表,则亦足以互相发明,而不害其为同也。”
其次,从诠释的角度来看,朱子对此章之诠释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以理学精神解释经典,体现出经典理学化的诠释特色。正如谢上蔡所言,对忠恕的理解难处并不在于训诂,而在于义理。近人程树德称,对此章义理理解主要存在两种意见,“此章之义,约之不外一贯即在忠恕之中及在忠恕之外二说。”①朱子从理学立场出发来解释忠恕一贯,认为忠恕即是一贯,忠为一为体,恕为贯为用,通过此章诠释阐发理学“理一分殊”这一重要思想。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尤其清代汉学家,多将忠恕看作行事,是“以尽心之功告曾子,非以传心之妙示曾子。”并批评《集注》“独借此大谈理学,”反映出与朱子不一样的诠释立场。
二是在继承前辈之说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理解,体现出精于择取而自出新意的特点。无疑,朱子对“忠恕一贯”的理解以二程思想为前提,但是我们应看到,朱子所选取的二程说是经过细致甄别选取的,剔除了其中认为不合适的部分,如他认为小程子引《孟子》“尽心知性”说、“忠恕贯道”说,《中庸》“君子之道四”说解释此章不可晓、有误。针对程门弟子各不相同的看法,他做出了精细的辨析取舍,特别是朱子采用《中庸》“至诚无息”诚本体说解释此章所蕴含的道之体用说,体现出他的创造性。
三是突出语境对文本的影响,讲究诠释的灵活性,以达到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的诠释目标。朱子有着明确强烈的诠释意识,认为诠释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将圣贤原义客观地挖掘呈现出来,以帮助学者加深理解。故此,他抓住“忠恕”在《论语》与《中庸》中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客观事实,指出二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指向,孔子之言与曾子之言深层原意各有不同,不可拘泥,亦不可牵合表层文字之同。学者应默识于言意之表,互相发明圣贤之意。
四是突出诠释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以达到针砭学弊,端正为学方向的诠释目标。划清儒学与佛老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纠正为学弊端,端正为学之方的诠释追求在这一章诠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子本章诠释,矛头指向空虚顿悟的禅学、舍本求末的浙东功利学,舍末求本的张、陆心学,要求学者树立本末兼顾,真积力久,由用达体的为学之方,提出尤其应在分殊上下工夫。
第四节 道统之两翼:《四书》与《太极图说》
宋儒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亲切体贴与创造诠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话语,朱子道统论是其中最具创见、意义深远的枢纽话语之一,亦是近来朱子学研究的热点话题。①本节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朱子道统世界究竟是如何构成的?朱子如何使道统思想的建构、《四书》新经典的诠释、理学思想的推崇三者相统一?如何看待周敦颐的道统地位?“太极”概念所代表的《太极图说》与《四书》在朱子道统世界中究竟居于何等地位?显然,朱子在一种注重文本诠释的看似保守的注述工作中,而寄托了极其新颖的理论创作活动,成功实现了中国经学范式从五经学向四书学的转移,并将宋学的精华——理学思想注入到了新经典体系中,从而既实现了经典再造,又做到了思想重构。用他的话讲,就是“刻意经学,推见实理”。朱子所成功开辟的这条经学再造与理学新思相统一的路线,真正实现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一致,挖掘其中的思想内涵,无疑对思考当下儒学经典诠释与思想创新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意义。
窃以为,朱子道统是由人物谱系、经典文本、核心范畴构成的精密系统,非止于《中庸章句序》“执中”之传。①它内蕴两条并行之路向:一可谓二程四书学工夫路线,其特点是认可二程传孟子之学,赋予《四书》以理学这一时代精神,突出格物等范畴的工夫教化意义。二可谓濂溪太极说路线,认可濂溪直传孟子之学。树立《太极图说》(含《通书》)为道学新经典,赋予太极范畴以形上本体意义。此“周程之学”体现了朱子道统中濂溪与二程、易学与四书学、本体与工夫的差异性和互通性,朱子有意强调了二者的独立性,其后学黄榦、程复心等则贯太极与四书为一,突出二者的一体性。朱子道统说正是通过对《四书》旧典的诠释与《太极图说》新典的推崇,树立了以周程道学精神为主导的道统谱系,形成了以《四书》和《太极图说》为主干的新经典范式,提出了一套涵盖工夫与本体的新话语系统,在继承之中实现了对儒学的更新和转化。
一 何谓朱子道统
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使用“道统”一词②,开篇即言:“《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③对“道统”与“道学”之定义及关系,学者有不同看法。陈荣捷先生区分了朱子道统的历史性与哲学性,强调了哲学性,肯定道统与道学的一体性。其《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言,“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性内在需要”。④余英时先生则从史家眼光出发,强调道统的外化和政治性,突出道统与道学、孔子与周公的差异性和断裂性:“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内圣外王无所不包……而孔子只能开创道学以保存与发明上古道统中的精义——道体,却无力全面继承周公的道统了”。①余氏突出道统与道学之辨,批评陈氏之说乃是采用后世黄榦之看法,混道统与道学为一。②且认为朱子道统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用意,据“《中庸序》推本尧舜传授来历”说,“完全证实了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是针对着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据比对《答陈同甫》与《中庸序》,认为“《中庸序》的道统论述是以该书为底本,已可以定谳”。③
余氏雄辩似有进一步讨论余地。首先,余氏对“道统”的考察可商。他认为朱子最早使用“道统”两字见于淳熙八年(1181)《书濂溪光风霁月亭》“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但“意指不很明确……大概此时他的‘道统’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④余氏之所以如此断定,是因为此处“道统”不合其心中“道统”必含政治之意,“道学”二字更合其意。其实,早在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榜文》中朱子已提及濂溪“心传道统”,即便在余氏认为朱子早已完全厘清道统与道学的绍熙癸丑(1193),朱子还是以“道统”称颂濂溪,《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言:“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可见,此道统并非一定含政治意义。朱子提及“道统”尚有以下五处,未见其必含政治义。己酉《答陆子静》“子贡虽未得承道统”⑤,丙辰《答曾景建》“况又圣贤道统正传”⑥,《语类》“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⑦,“则自汉唐以来,……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⑧,绍熙五年《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恭惟道统,远自羲轩”。①朱子《中庸章句序》认为孔子不仅不是所谓“道统的无力继承者”,反而是集大成者。颜、曾、思、孟传承光大道统,濂溪二程接续之,朱子本人亦“赖天之灵,幸无失坠”。《章句序》末言“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可见朱子隐然以传承道统自居。
其次,余氏认为朱子道统针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恰与朱子道统的“去政治化”用意背道而驰。《中庸章句序》所论道统的演变与《大学章句序》大体相同,朱子认为,孔子不得其位并没有妨碍其成就,他反因继往开来之贡献越过了尧舜,以学统的形式延续了道统,使借助学统形式所表现的道统依然保持了其独立性和超越性。朱子的道统与道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合②,孔子之后所传道学即道统之根本所在,即便是道统所涉帝王之治,亦当在道学范围内,如帝治当以格物正心为本。朱子坚持认为政治上的成就不能作为判定得道与否的标准。当弟子质疑“天地位万物育”仅指当权者时,朱子指出,反躬自修的穷乡僻壤之士亦能做到。③此与宋明儒学走向平民化、内在化的趋向一致,如过分突出道统的政治向度,则显然与此大趋势背道而驰。如余氏之解,则孔子以下已无“道统”可言。④
余氏为突出朱子道统的政治义,认为《中庸序》以乙巳(1185年)《答陈同甫》“来教累纸”书为底本的“定谳”恐难为“定谳”。然此书与《中庸章句序》仍有少许距离,而《戊申封事》及同时若干材料则几与《章句序》全同。⑤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子《中庸序》亦经反复修改而成,朱子癸巳(1173年)为好友石子重所写《中庸集解序》实为《章句序》之早期底本①。比较二序可知,其差别主要有二:其一,《集解序》仅从孔、曾、思、孟立论,未提及《章句序》尧舜禹汤等孔子之前道统谱系,此是一大变化。其二,《集解序》特意点明“濂溪周夫子”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道统枢纽地位,但《章句序》则只字未提。《集解序》还特意批评汉唐诸儒,尤其点出了李翱,此亦不见于《章句序》。
综上,笔者以为,陈荣捷先生从哲学角度判定朱子道统论更合乎实际。简言之,朱子道统指道之统绪,当含传道之人、传道之书、传道之法。其内容实由两条并列线索构成:第一个路向以二程为传人,以《四书》为载体,以工夫范畴为根本,其要乃在日用工夫。第二个路向以濂溪为传人,以《太极图说》为载体,以太极范畴为根本,其要乃在形上本体。
二 二程《四书》工夫道统论
(一)宗二程为统
朱子道统论具有树立道学正统,维护道学纯洁的目的。其道统谱系从立正统与判异学两面展开,立正统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一是尊孟退荀,二是摆落汉唐。三是宗主二程。需要说明的是,朱子虽对张载、邵雍、司马光之学亦有认可吸收,然亦不乏否定,较之二程,他们终是偏颇。朱子道统的“正统性与纯洁性”见诸其强烈的推崇洛学的学派意识,仅据《六先生画像赞》、《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并不能表明朱子认可张、邵、司马接续道统。此三种文字并未论及道统,且皆作于朱子道统思想尚未形成的癸巳前后。除《画像赞》外,余二者皆受吕祖谦很大影响,并非纯为朱子意。②四是排斥程门而自任道统。朱子不仅对汉唐诸儒未能传道不满,更明确表达了对二程之后百余年间道统传承的失望。尽管二程弟子众多,但朱子认为“多流入释氏”,未能接续二程之道,“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③当仁不让的认为自己虽私淑二程,却能接续其学。故《大学章句序》丝毫不提二程后学,直接自任接续二程之传。“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中庸章句序》直斥程门“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朱子道统论极其注重门户清理,即便理学内部,亦严加甄别,其“道学”所指含义甚窄。《宋史·道学传》于朱子同时学者,仅列南轩,而置陆九渊、吕祖谦于《儒林传》,实据朱学立场。
在树立正统的同时,排斥“异学”亦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使命所在。《学庸章句》二序皆特重判教,此判教当分三层:最要者是“弥近理而大乱真”的佛老之学,第二层则是与儒学有各种关联的流行之说,俗儒记诵词章之习,权谋术数功名之说,百家众技之流。凡非仁义之学,皆在批评之列。朱子一生与人发生多次学术辩论,即与此有关。第三层则是渗入儒学内部的不纯洁思想。朱子对此尤为关注,早年所撰《杂学辨》即批判吕本中、张九成等前辈学者溺于佛老,陷入异端。丁酉《四书或问》对程门诸子严加辨析。于同时代学者,尤为痛斥陆九渊之学流入佛老异端,实为“告子之学”。但朱子通过判教所树立的“道学”,当时即引起时人不满,陆九渊即对朱学树立门户、张大“道学”一名深表忧虑,言“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①道学之外的周必大亦对此严加批评。②
(二)推《四书》为经
朱子在继承二程表彰、阐发《四书》的基础上,首次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一有机整体而加以全面注释,最终使“四书学”取代“五经学”,成为宋末以来新的经典范式。朱子对《学》、《庸》、《论》、《孟》的特点有清晰把握,指出《大学》通论纲领,阐明为学次第,亲切易懂,确实可行,在四书系统中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首要意义。《论语》多为对日用工夫的即兴阐发,可树立为学根本,但文字松散,义理不一,故初学不易把握。《孟子》则注重对义理的发扬阐发,易于感动激发人心;《中庸》工夫细密、规模广大、义理深奥,多言形上之理,最为难懂,故作为《四书》的殿军。“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①朱子自认用功最多,成就最大者为《大学章句》一书:“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②他将《大学》视为《四书》枢纽,认为实质上起到对其他三书的贯穿作用。常以“间架”“行程历”“地盘”“田契”“食次册”等形象说法强调《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纲领地位,《论》、《孟》、《庸》可以说皆是《大学》的填补与展开,但从义理言,《四书》各书无有高下之分,他批评了《论语》不如《中庸》的观点。
就《四书》与五经的关系,朱子多次从工夫简易、义理亲切的角度肯定《四书》在为学次序上先于五经。当由《四书》把握为学次第规模、义理根源、体用纲领,再进而学习六经,方能有得。他以“禾饭”“阶梯”“隔一二三四重”的形象譬喻传达了二者在教法、效用上存在难易、远近、大小关系。“《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③“四子,六经之阶梯。”淳。④朱子以自身为学实践为例,甚至将经学所得比作“鸡肋”,以此告诫学者,不应重蹈其覆辙,而应直接就《四书》现成道理探究。朱子继承发展了程子“《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知而明”的思想。认为《四书》作为阐明义理之书,对其他著作的学习具有标尺意义。掌握了《四书》这个义理中心,就等于掌握了根本,由此理解其他一切著作,皆甚为容易。故他对《四书》穷尽毕生精力,每一用语皆费尽心力,称量轻重适中,方敢写出,生怕误解圣贤本意。连无关紧要的虚词,亦反复掂量,以达到丝毫不差的精细地步。
(三)以工夫传道统
朱子注释《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落实道统观念,以道学思想规定道统内容。《四书集注》始于道统、终于道统,《大学章句序》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道统,《孟子集注》终于明道接孟子千年不传之学。从道统传道人物来看,孔、曾、思、孟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传承四子思想的经典相对应。学界对朱子道统的认识通常局限于《中庸章句序》之十六字心传,此“执中”之传仅为《四书》道统之一部分,仅以精一执中之传无法限定、解释朱子广大精密的道统系统。我们将视野拓展至全部《四书集注》时,发现其中充满了朱子的道统观。《中庸章句》开篇序引程子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强调子思传孔子之道于孟子,其要在理事、一多范畴。《中庸》实以道之体用为中心,费隐章、诚明章作为管束全篇之枢纽性章节,皆阐明此意。《论语》亦多处论及道统之传。《论语集注》点出颜子、曾子对夫子之道的领悟与承当,“忠恕一贯”是“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是曾子传道工夫根本所在。“克己复礼”被称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体现了儒家道统之孔颜授受,朱子数次将之与精一之传相提并论。此外,朱子对“斯之未能信”“曾点气象”“逝者如斯夫”等章皆是从见道、体道角度阐发之,指出此皆关乎道之体认与传承。《论语集注》末“允执其中”章引杨时说,言《论语》、《孟子》皆是发明儒家道统之书,指出圣学所传,乃在中道。《大学章句序》以性气之别为理论基础,逐层阐明以复性之教为中心的儒学道统论,建构了由政教合一至政教分离的道统演变史,批判了道学之外佛老、词章、功名等诸说流弊,突出了二程及朱子传道地位。强调《大学》格物、诚意直接贯通道体,是能否传承道统的工夫要领。朱子将《孟子》列于《四书》,决定性地结束了孟子地位之争,确定了孟子道统地位。《孟子集注》称赞孟子仁义论、性善论、养气论皆是发前圣所未发之论。把尧舜性者章上升到传道高度,称赞明道对尧舜与汤文武性之、反之的二重判定极为有功,显示明道学达圣域,否则不足以言此。末章点明孟子依次序列群圣之统绪,表明先圣道统传承所在,将传诸后圣而永不坠落。
朱子尤重以工夫论《四书》,正如学者所论,朱熹的《四书》学“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①故对工夫范畴的阐明,既是朱子理学思想要领所在,亦是其道统论根基所在。在朱子看来,工夫实践是第一义的,无体道工夫,则不可能领悟道,更无法传承道统。《四书集注》创造性地诠释了《四书》系列工夫范畴,与道统最密切者有主敬、格物、诚意、慎独、忠恕、克己等。
朱子对十六字心传的阐发围绕存理灭欲的存养省察工夫展开。不仅尧舜禹汤孔子等以精一执中工夫传道,颜、曾、思、孟亦皆以各自入道工夫传承道统,无工夫则无法传道。其《答陈同甫》先阐发十六字心传精一工夫,紧接着指出夫子于颜、曾、思、孟之传亦是如此,四子分别以各自工夫传道,颜子以克己、曾子以忠恕、子思以戒惧、孟子以养气,鲜明体现了儒家工夫道统相传之妙。主敬是朱子的工夫要旨。朱子视敬为成就圣学必备工夫,始终深浅,致知躬行,无时无处不在,称赞敬为圣门第一义,为工夫纲领和要法,“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①多次从工夫道统的角度论敬,指出尧舜以“敬”相传,敬贯穿圣人所有言行,为其作圣根本。“圣人相传,只是一个字。……莫不本于敬。”②程子以敬接续道统。“至程先生又专一发明一个敬字。”③强调程子对敬的发明远迈前人,盖圣人只是论说“敬目”,而未曾聚焦于“敬”自身意义,程子将“敬”脱离具体语境,突出为独立的具有本体意义的修身工夫,“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④朱子认为可由敬而入道、传道,尽管颜回克己与仲弓敬恕工夫存在高下之分,但敬恕亦能达到无己可克的人道境界。
格物是朱子工夫论的核心概念,朱子从道统高度来认定格物的意义。言:“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曾说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无复遗虑。然程子既没,诸门人说得便差,都说从别处去,与致知、格物都不相干。”⑤朱子对韩愈道统地位排斥的一个重要根据,即是基于其对“格物”的忽视,格物是入道必经之门,无格物者,其所有工夫只是一“无头”工夫。在朱子看来,忽视格物工夫的学者没有资格纳入道统谱系,这极大强化了道统的道学属性。朱子推崇程子格物说,批评程门亲传弟子未能传承发挥其格物工夫,故未能接续道统,而自身则上接二程格物,故得承道统。朱子的格物之学乃围绕成就圣贤展开,只有为圣贤之学服务,格物才可能“是(朱子)他全部哲学的一个最终归宿。”①《四书集注》据格物以阐述孔、曾、思、孟圣贤境地,充分显示了格物贯穿全书的枢纽地位。朱子对“诚意”之重视与开拓,绝不亚于“格物”,提出“诚意”是“自修之首”,是衡量修养境界的根本标准,是人鬼、善恶、君子小人、凡圣的分界点,“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②。“诚意是善恶关。……诚意是转关处。……诚意是人鬼关!”③“知至、意诚是凡圣界分关隘。”④朱子释诚意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⑤此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一于善”,意有善恶之分,故需要诚之实之功夫来贞定意念的价值指向,使所发意念皆归于善。用“一”,强调了意念归于善的纯粹性、彻底性、连续性。“善”则指明了意念的性质。诚意之学于朱子学术、人生、政治皆具有某种全体意义。它不仅是朱子诠释的对象,更是一生道德修养之追求。朱子以“格君心之非”为治国之纲领,将“诚意毋自欺”视为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根本,多次向帝王上书强调诚意正心之学的重要。第二层是诚意蕴含慎独,《大学》、《中庸》皆言及慎独工夫,慎独是谨慎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而审其几。《中庸章句》指出慎独是在心之未发已发之际的工夫,在隐秘幽暗的状态下,审视事物之几,以遏制人欲于萌芽状态。能否实现诚意,做到中道,皆取决于慎独。如上两节所述,关于颜子“克复心法”、曾子忠恕之传,皆是突出了二子修身工夫之重要,故可视为“十六字心传”之重要补充。
三 濂溪《太极图说》形上道统论
(一)以濂溪为统
濂溪在朱子道统中的地位,是一让人颇感困惑的老问题。陈荣捷先生指出,朱子道统论最要者在此,最困难者亦在此,《新道统》言:“乃孟子与二程之间,加上周子,此为道统传授最重要之改变。”①“朱子此一抉择,至为艰难”。②最争议者依然在此,“此为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争论未已”。“所谓两程受其学于周子,殊难自圆其说”。③认为朱子将濂溪列入道统纯粹出于哲学(处理理气关系)而非历史原因。然朱子对濂溪的态度亦令人无所适从④:一方面,朱子明确二程直接孟子之传,如阐发道统说最要的《学庸章句序》丝毫未提及周敦颐,但癸巳《中庸集解序》曾明确濂溪上接孟子而下传二程,“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如何至于后来,反而删除之?或许,如于《四书》中确认濂溪上接孟子,则很难在《四书》系统内解释濂溪对孟子的继承和对二程的开启,亦将与二程不由濂溪而上接孟子的说法相冲突,盖在二程道统谱系中其实并无濂溪位置。程颐为明道所作《墓表》言:“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明确宣称自悟“天理”而非“太极”本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⑤此或《四书》道统添入濂溪困难所在,故朱子干脆删除之。⑥朱子将濂溪从《四书》工夫道统剔除并不意味着置濂溪于道统之外,其他相关文字反复推尊濂溪得孔孟道统之传而开启二程,具有如夫子般“继往开来”之地位。在淳熙四年至十年所撰五处濂溪祠堂记中,朱子皆阐明濂溪的传道枢纽地位。如淳熙四年《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言:“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与。”①五年《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言:“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河南两程先生既亲见之而得其传。”②六年《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则将濂溪太极说与《四书》联系起来,认为太极之说实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在传承,完全合乎圣人之言,以称颂孔子的“继往开来”来称赞濂溪,视其为旧儒学之接续,新儒学之开创者,在道统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③八年《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则进一步将濂溪太极之学与《四书》工夫道统相贯通。指出濂溪学主旨是格物穷理,克己复礼,实与《四书》内在一体。“诸君独不观诸濂溪之图与其书乎!……然其大指,则不过语诸学者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④十年《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更进一步,从明天理、传道学的角度称颂濂溪,概述其阐明天理本体、揭示克复作圣之功的本体与工夫两面贡献,孟子以下,一人而已,开创儒学复兴新局面之功无人可比,评价无比之高。“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盖自孟氏既没,而历选诸儒授受之次,以论其兴复开创,汛扫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⑤可以看出,朱子数篇祠记对濂溪的评价,时间愈后,评价愈高,定位于继孔孟而开二程,并有意将其太极本体理论与四书工夫理论相关联。
与《四书》道统不提甚至撇开周程关系不同,朱子晚年两篇文字中特别提出“周程”说,强化二者授受传承关系。绍熙癸丑(1193)《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直接提出周程接续孟子之道,“自孟氏以至于周程”。⑥绍熙五年(1194)《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强调周、程“万理一原”的道统传承,祭祀圣贤的释菜之礼,亦以濂溪、明道配。“周程授受,万理一原。”但朱子强化周程授受关系的看法曾遭到好友南轩、汪应辰等质疑。他们认可二程早年受学于濂溪这一事实,但并不认同二程传濂溪之道,最根本的是二程不认可这一点,且对濂溪似有不敬。①二程与濂溪的理论路线、经典取向并不一致,二程更重视《四书》的工夫教化论,由工夫而领悟天理本体。即便伊川重视《易》,其路向亦与濂溪亦迥然不同。为此,朱子坚持论证濂溪传道二程,认为当从不受重视的《通书》入手,方可看出二程得濂溪之传而广大之。朱子提出二程阴阳之说、性命之论等皆受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影响,根据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定性书》、《李仲通铭》、《程邵公志》,此种《铭》、《志》论述实不足为据。至于《好学论》、《定性书》是否在精神实质上与濂溪一致,亦可商讨。朱子己丑(1169)《太极图说》建安本序认为,二程性命之说来自《太极图》、《通书》,具体证据是《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与二程的一《志》、一《铭》、一《论》关联密切。己亥(1179)南康本《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主张二程论述乃是继濂溪《太极图说》、《通书》之意,一《志》、一《铭》、一《论》尤其明显,不仅师其意,且采其辞,更外在化。有学者认为二程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②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二程因受学于濂溪而得孔孟之传,且传其《太极图说》、《通书》,突出了周程授受对于二程道统地位确立具有决定性地位。可谓无濂溪之传,则二程不可能得传道统。二程之外,亦无人能窥濂溪之意,故二程没而其传鲜。此既突出了濂溪悟道之高,又点出周程授受之唯一性。朱子解答南轩二程未道及《太极图》的原因是“未有能受之者”,骤然传之,反致不良影响。
朱子以濂溪《太极图说》为主的道统论①,在人物谱系上突出了伏羲和濂溪,在经典文本上以《太极图说》为中心,在范畴诠释上彰显了“太极”的形上意义,为朱子理学本体论建构奠定了根基。朱子以“同条而共贯”说阐明以太极为中心的道统论,指出伏羲易始于一画、文王易开端于乾元,太极概念始于夫子,无极、《太极图》则濂溪言之。四说虽异,其实则同,关键在实见太极真体。《答陆子静》言“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②朱子比较了伏羲与濂溪之学,判定濂溪太极图是自作。以阐发易学大纲领,义理精约超过了先天图,但规模不如其弘大详尽,故仍处先天范围内,而无先天图之自然纯朴。《答黄直卿》言:“太极却是濂溪自作,发明《易》中大概纲领意思而已。故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之精而约。”③
(二)《太极图说》的本体论
朱子哲学体系主要通过诠释濂溪《太极图说》形成。前辈学者冯友兰、钱穆、陈荣捷等早已指出朱子哲学与《太极图说》的密切关系。陈来先生指出,“朱熹以太极为理,利用《太极图说》构造理学的本体——人性——修养体系,这是理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④以下讨论朱子对太极、诚、圣人三个相应概念的阐释。朱子是理太极的代表,把太极解释为理,视为理之极致,“(太极)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⑤又认为太极只是指示万善总会的表德词。“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⑥太极还是生生无穷之理,是万物产生之本根,“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太极图解义》认为太极作为阴阳动静根源之本体,并不脱离阴阳而孤立,是即阴阳而在之本体,突出了二者的不离不杂。朱子分析了太极本体与分殊之理的关系。《太极图说解》的“统体太极”和“各具太极”阐明了作为万理之源的太极与无数分理的关系。自男女、万物分而观之,各具一太极,全体合观,则是统体太极。此两种太极在理上并无不同。朱子人性论以太极阴阳的理气同异说为理论基础。人物禀太极之理而为性,禀阴阳之气为形,此理气凝聚构成人之性形。人物性同气异的原因在于:人物皆具同一太极之理,在气化过程中,只有人禀赋阴阳五行之灵秀,故人心最灵妙而能保有性之全。在人性论上,朱子主张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所谓气质之性,乃是作为太极全体的性落入气质之中,它并非天命之性的另外一种,而是天命之性的一种现实形态。朱子追溯此论之源头,认为孔孟虽内含此说,然程、张因濂溪方才发明此说,程子性气之论来自濂溪,若无濂溪太极阴阳说,程子无法提出此说。“此论盖自濂溪太极言阴阳五行有不齐处二程因其说推出气质之性来,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①总之,朱子对濂溪《太极图说》太极本体论思想的挖掘,构成其道统论的本体面向。
立人极之圣人。《太极图说》下半部分论述了太极的人格化——圣人,是太极思想在人道领域的落实。②圣人是太极的人格化,全体太极之道而无所亏,保全天命之性而无所失,定其性而不受气禀物欲影响,故能树立为人之标准。朱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全体太极”以定性,以立人极。圣人在德性上具有如太极般的全体性(全具五常之德)、极至性(中正仁义之极)、自然性(不假修为)。“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通书》对圣人特点发明详尽透彻。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实理性、太极的浑然全体性。“孔子其太极乎!”通变无碍性,“无不通,圣也。”“大而化之”的“化”性。“圣者,大而化之之称”。朱子《四书》对“人极”亦有论述,《学庸章句序》皆以“继天立极”开篇,其“立极”当指“立人极”。“继天立极”指圣人继承天道以挺立人道,此立人极者亦即尽性者,故天命为君师教化民众以复其性。《四书集注》亦多次以“太极”解释夫子之圣,圣人是天理、天道之化身,如太极一体浑然而备阴阳正气,动静行止,皆如太极动静之显发。其外在容貌间所呈中和气象,显与天合一之境界。“子温而厉”章注:“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
“诚,即太极,圣人之本。”诚被朱子视为与太极、圣人对应的本体概念,诚是“实理”。圣之为圣的根据就在于诚。诚具有太极、圣所共同具备的特点:全体、内在、超越、自然、通化等。《通书》乃发明《太极图》的表里之作,首章“诚”完全对应于《太极图》,朱子《通书注》说,“诚即所谓太极也”。诚之源为“图之阳动”;诚斯立为“图之阴静”;诚之通、复为“图之五行之性。”诚是圣人的独特属性,只有圣人能保全此诚。“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诚的本来意义是真实无妄,其形上意义则是天命之性(理),是事物内在禀有之理。朱子强调了诚的实理性,万物资始是“实理流出”,各正性命是“实理为物之主”,纯粹至善是“实理之本然”。认为《通书》“诚神几曰圣人”的诚、神、几分别指实理之体、实理之用、实理之发见。指出诚具有自然、简易的特点。“诚则众理自然”。但诚与太极、圣人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它还有工夫意义,是贯通天道与人道的连接者。朱子明确区分了诚的这两层意义:《中庸》的至诚指“实有此理”,诚意则是工夫之诚,不欺之诚。汉唐学者皆以忠信笃实之德言诚,朱子称赞二程以实理言诚实为创见,并提醒要兼顾诚的这两层含义。“诚,实理也,亦诚悫也。由汉以来,专以诚悫言诚。至程子乃以实理言。”①
(三)推《太极图说》为经
朱子通过精心诠释和大力推崇,将《太极图说》树立为道学首要经典,指出《太极图说》是言道体之书,穷究天理根源、万物终始,自然而成,并非有意为之。《与汪尚书》言:“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①认为该书对工夫问题论述甚少,仅限于修吉、主静,朱子则将主静转化为主敬,他高度评价《太极图说》、《通书》,认为所论如秤上称过,轻重合宜而精密无差。“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轻重极是合宜。”②视《太极图》、《西铭》为孟子之后儒家最好著作,甚至认为《通书》比《语》、《孟》尚且语义分明,精密深刻,布局严谨。“《通书》比《语》《孟》较分晓精深,结构得密。”③淳熙丁未(1187)《通书后记》强调濂溪之书远超秦汉以下诸儒,条理精密、意味深刻,非潜心用力,不能明其要领。认为《太极图》具有首尾相连、脉络贯通的特点,《图说》上半部五段对应五图阐发了太极阴阳生化过程;下半部分论人所禀赋的太极阴阳之道,与上半部相应,体现了天道人道一体的观念。首句一一对应上半部分,人之秀灵即是太极,人之形神则是阴阳动静,五性则是五行,“善恶分”则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事出”为万物化生。自此而下的“圣人定之”句,体现圣人得太极全体,而与天地混融为一,实现了天人相合。故《太极图说》与《中庸》皆阐明天人合一、贯通形而上下这一主题。
朱子强调《通书》围绕太极这一核心概念来发明《太极图》之蕴,透过《通书》方能清楚把握《太极图》的主旨,若无《通书》,则太极图实不可懂。“《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④《通书后记》指出《通书》和《太极图说》是表里关系,是对《太极图说》太极阴阳五行的阐发,实为道体精微之纲领,并强调了义利文道之取舍,以圣人之学激发学人走出功名富贵文辞卑陋之俗学,对为学工夫、治国之方皆有亲切简要、切实可行的阐述。朱子早在己丑《太极通书后序》就指出《太极图》是濂溪之学妙处所在,《通书》用以阐发《太极图》之精蕴。淳熙己亥《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进一步指出《通书》诚、动静、理性命三章尤其阐发《太极图》之奥妙。还以“诚无为”章具体论证与太极阴阳五行说的对应。《近思录》开篇所选周子说,亦是《太极图说》与本章,可见朱子对此章之重视。①朱子对《太极解义》极其满意,认为恰到好处地阐发了濂溪之意,达到了“一字不可易处。”②朱子可谓对濂溪《太极图》用力最深,最有创见者,采用章句分解形式,以注经的严谨态度疏解此书,最终使得该书层次分明,粲然可读。经由朱子的大力推崇,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太极图说》道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四 工夫与本体:《四书》与《太极图说》的贯通
(一)《太极图说》与《四书》的贯通
朱子广大的道统体系由《四书》和《太极图说》所代表的工夫、本体双主线构成,二者相互贯通,体用一源,工夫是通向本体之理的手段,本体是分殊工夫的最终实现,工夫不离本体指引、范导,本体端赖工夫真积力久,可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朱子阐明了《四书》与《太极图说》的密切关联。《四书》虽以日用工夫为主,然工夫以太极本体为理论基础,指向道体之领悟。如朱子的格物穷理就是通过不断穷究事理,积累贯通,达到豁然开悟,物理明澈,心与理一的心体光明状态。《大学或问》以《太极图说》无极二五的理气说解释人物之性形。天道流行发育,以阴阳五行作为造化之动力,而阴阳五行的出现又在天道之后,盖先有理而后有气,故得理为健顺五常之性,得气为五脏百骸之身。《中庸章句》多言形上之道,其性、体用、诚论,皆与《太极图说》息息相通,不离理气先后、理气离杂、理一分殊、理气同异、天人一体等命题。如首章指出性专言理,道兼言气,在道的意义上是理在气中而理气不杂,正如太极阴阳之不离不杂。采用太极阴阳五行解释健顺与五常,性即太极,健、顺分指阳、阴,仁义礼智对应五行,将人性健顺五常与太极阴阳五行严密对应,体现了天人的一体性。以理一分殊、理同气异解释《中庸》性、命之说。凡涉及人物之性,皆以性同气异、理一分殊解之。从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释“不诚无物”,强调理在物先,理内在包含了物。朱子同样以理一分殊、理同气异释《论孟》重要章节。如提出忠、恕分指理一分殊、体用、天道人道,忠是理一,恕是分殊,忠为恕体,恕为忠用,忠指天道流行,恕则各正性命。以理一分殊说阐发见牛未见羊章、君子之于物章所体现的儒家之爱的差等性与普遍性,以理气先后阐发浩然之气章、性命章、异于禽兽章、生之谓性章等,特别提出儒家人性思想直到周子太极阴阳五行说出,方能阐明性同气异,程、张人性论皆是受濂溪阴阳五行说影响,突出了濂溪的开启之功。“及周子出,始复推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则同,而气质之所从来,其变化错揉有如此之不齐者。……此其有功于圣门而惠于后学也厚矣。”①“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②尽心知性章引张载说,并将之与《太极图》相对应,太虚即《太极图》最上圆圈无极而太极,气化之道即阴阳动静。
(二)朱子后学绾合《太极图说》与《四书》
朱子后学基于朱子对《太极图说》与《四书》内在关系的阐发,进一步绾合二者,树立了《太极图说》与《四书》为源与流、本体与工夫关系的认识。黄榦是阐发朱子道统论最有力者,对此亦多有阐发。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指出:
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赋于人者秀而灵。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物之生也,虽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人中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尧之命舜,则曰“允执厥中”中者……则合乎太极矣。③此以《太极图说》的太极阴阳五行论儒学道统,太极二五理气之合而生人物,人得其精气而秀灵,虽物之偏塞亦皆不离太极。圣人则是人中最秀灵者,故能继承天道以确立人极,而获道统之传。此一论述完全将儒学道统置于太极本体的天道基础上,与《尚书》“十六字心传”置于圣人之传不同,突出了道乃是合乎太极本体,因应万物生成而来。勉斋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周、程、朱子道统之传,多以《四书》一二核心工夫词概括之,且皆与太极相合,体现了勉斋以工夫为重的道统特色。显然,勉斋所建构的工夫道统,确有其“武断”,然此“武断”把握了道学重视下学上达的道统特色。勉斋另一鸿文《朱先生行状》则有意区别了朱子的为学与为道,指出其为道是以太极阴阳五行论天命性心五常之德:“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①可见勉斋始终置太极之学于道统之首,此亦正合乎陈荣捷先生以补入太极为朱子道统观念最具哲学性之改变的看法。
元代朱子后学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亦将《太极图说》与《四书》,太极与道统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结合。他在全书开篇处即采用十节图文依次论述从伏羲到朱子的传道系统,尤以《太极图说》为中心,突出了周敦颐与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指出程子去世后,周程所接续的以太极为核心的儒家道统面临中断危险,幸得朱子重新对周程易学作了深入阐发,学者如能反求诸心,以主敬为工夫,则能体悟太极内在于人,实为心之妙用,故以太极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实皆本诸于心。“又幸有朱夫子以发其精蕴,学者苟能求之于心,主之以敬,则知夫太极者,此心之妙用;《通书》者,又太极之妙用。”此把主敬工夫与太极本体相贯通。复心通过横渠、朱子说以证明二程在太极阴阳这一传道核心上与濂溪所接续伏羲之传一致,并以此作为列《太极图说》于《四书章图纂释》之首的原因。特别表明本书将《太极图说》置于编首的意图,意在显示周子《太极图说》端为《四书》道统之传、性命道德之学的本原所在。“故特举先生《太极图说》于编首,以见夫《四书》传授之奥,性命道德之原,无一不本于此《太极图说》”。既然周子是通过对作为《四书》源头的“太极”的图说来阐发、接续儒学之道,那么对作为“太极”之实质传承的《四书》自然亦可以“图说”了,此即其图解四书,“立图本始”所在。
在《太极图说》《四书》与朱子道统关系上,我们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夸大《太极图说》代表的道统对于《四书》道统的“纲领性”和“含摄性”。如有观点认为,“朱熹本于易道,起自伏羲的道统可以含摄本于《尚书》起自尧舜的道统”。①其实《太极图说》与《四书》道统分别侧重道统本体向度和工夫向度,二者可谓源流关系,理一分殊关系,不可偏废。如就朱子终生奉为圭臬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之教而言,他当更重视下学一面的《四书》道统。盖朱子哲学“非以本体论宇宙论为归宿,而重点在乎人生,即在乎《四书》之教。”②二是日本学者山井涌教授因《四书集注》未见“太极”而提出太极于朱子哲学并非重要的结论,陈荣捷先生作《太极果非重要乎》驳之,认为“太极乃本体论与宇宙论之观念,而《四书》则勿论上学下学,皆针对人生而言。”③其实,太极概念未见《四书集注》极为正常,此符合朱子不以难解易、不牵扯它书的解释原则。如朱子批评南轩《孟子解》的重大失误在于以太极解性,“盖其间有大段害事者:如论性善处,却着一片说入太极来,此类颇多。”④太极在朱子看来,其实为理,故朱子虽论太极不多,然处处论理,善观者当就朱子论理处观其太极说,而非必紧盯是否出现“太极”之名。盖一则太极经朱子之诠释、辩论而得以形成理学之最高概念,它本不如理、仁等概念易知;二则太极为形上抽象概念,属于儒者罕言的“性与天道”之范畴,朱子虽以太极为其哲学基石,然其教之重心,仍在《四书》的分殊工夫一面。故由朱子罕言“太极”之名不等于朱子罕言“太极”之实,亦不等同太极于朱子并不重要。
总之,朱子不仅使道统成为一个新范畴,而且使之成为一个工夫与本体兼具、天道人道并贯的广大精密系统,它含摄了朱子理学形上建构和形下实践的核心范畴。朱子的道统世界实现了思想建构与经典诠释、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一方面,他以极具时代感的道学精神诠释《四书》原典,使先秦《四书》与作为时代精神的道学融为一体,随着《四书》成为新的经典范式,道学亦实现了其经典化,成为儒学新发展之主干。另一方面,他极力推尊周程,精心诠释道学著作,使《太极图说》成为足与《四书》相当的道学必读经典,构成了以《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为主的道学新经典,道学文本的经典化极大树立了道学的权威地位,强化了道统的道学特色。朱子的思想建构依托于对道学范畴的创造性诠释,他的道统世界奠基于对道统、太极、格物等系列范畴的开创性诠释上,这些范畴与其经典诠释浑然一体,影响了身后数百年儒学的发展,是贯穿后朱子时代理学发展的主线,直至今日仍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转化不可或缺的资源。
第五节 道统的“门户清理”
在朱子漫长的为学历程中,从学李延平是个极重要阶段,它促使朱子断绝了对佛学的留恋,走上了以“四书学”为学术重心的圣学之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其重要标志是朱子于延平去世后不久即撰成清理儒学内部阳儒阴佛思潮的《杂学辨》,该书尤以对张九成《中庸解》的批判为中心。朱子的辨张无垢《中庸解》实为其早年思想的一次重要总结,在其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不可忽视的意义。故本节以《杂学辨》中辨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阐释朱子对《中庸》性道、戒惧、忠恕、诚、知行诸核心概念的认识,揭示其此时的中庸学水平,阐发其辟佛老、重章句的学术风格。参照晚年对《中庸》之论述,可以清晰地揭示朱子早年中庸学的得失、因袭、修正之处;这同时又是朱子在完成自我修正后对洛学门户的一次大清理,集中展现了朱子的佛教认知,显示了朱子的强烈卫道意识。故探讨该书,可以充实丰富朱子早年学术思想研究,对把握朱子思想的演变、朱子的道统意识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朱子辨无垢《中庸解》乃是接着从学延平而展开的,故先略述延平对朱子中庸学的影响,然后展开朱子对无垢《中庸解》批评的论述。论述以相关概念为主,重点在三个方面:朱子此时中庸学水平与晚年的异同比较;朱子此时对佛学的认知态度;朱子的解经方法始终表现出对章句之学的重视。透过历时演变的眼光看待朱子思想的因袭变化,阐明其道统思想的辟异端之面向。
一 “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朱子在从学延平之前就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受到正统有序的理学教育,他曾说自己十六岁就知理学是好东西。因家学和师长的熏陶,自小熟读《中庸》。与此同时,亦接触到禅学,并一度对之迷恋,早年诗作《牧斋净稿》即是明证。故当他二十四岁拜师延平后,延平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以所传“龟山指诀”,将其引导到理学正轨上来,分辨儒佛之异。延平为龟山高弟罗从彦之徒,得道南一脉之传,为学特重《中庸》,称赞该书将儒家成圣之学的工夫路径显示得清楚详尽,毫无遗漏。《延平行状》说:“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①延平思想最大特色在于从未发已发入手,通过静坐涵养的工夫,来体认未发之本体,由此达到切实自得、气象洒落之境界。“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②故其对朱子之教育,反复谆谆于“涵养”“体认”,惜乎朱子对此“龟山指诀”实不相契,转而喜从逻辑分析、章句考论入手,故二人于《中庸》章句之学讨论甚多。朱子此前因学禅之故,对本体思想有所了解。李侗为扭转其好佛趋向,授以儒学理一分殊之学,特别揭示分殊的重要,使朱子获知儒学体用不二、超越内在之精义,此点对其弃佛归儒影响甚大。概言之,此时朱子的中庸学具有以下特点:
在工夫进路上,特别注重道问学的一面,坚持认为道问学有其独立价值,是为道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夫(这一点与今人重逻辑分析之学相似)。朱子中庸学的一大特色就是自始至终注重章句文本之学。延平则认为为道“非言说所及也”,告诫朱熹“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而朱熹则“窃好章句训诂之习”,认为不展开谈说论辩,则于道理看不分明,于工夫偏颇不全。故晚年尚从为学博约并进的角度,当弟子面公开批评延平之学缺乏辨名析理的问学工夫。“然李终是短于辩论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①然而延平对涵养践履的强调,对朱熹形成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为学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本体论上,朱熹接受延平理一分殊之教,将之与对《中庸》中和的理解结合之。朱熹对延平“分殊”之教,尤有深刻感受,曾反思在见延平前自身为学染有一般学者通病:喜好笼统、高远、宏大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②而延平则教以“所难者分殊耳”。正是延平“所难之分殊”改变了他的为学方向,并成为他一生评判学术的标准。
此时朱熹自觉运用理一分殊之学来理解中庸(仁)。在对《中庸》性论的理解中,将理一分殊与未发之说结合起来。他说,“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窃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未发时看”。(先生抹出批云:“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③朱子认为,在理(性)一的意义上,生物皆同,在气禀(分殊)的意义上,人物有别。“理一分殊”表述的是理的本然状态,当从五常之性、本体未发时看待。延平则主张不能仅从未发、性内的割裂观点来看,当兼顾已发、外在,从全体连续的视角展开。朱子此时习于将仁与未发比配,如他认为“肫肫其仁”反映出全体是仁的义理,只有尽性之圣人方能做到。“全体是未发底道理,惟圣人尽性能”。延平则认为此是讲工夫所达的境界,不是谈义理。“乃是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④朱子对鬼神章的解释,亦是从“理一”这个本原兼含已发未发来看,“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窃谓此章正是发明显微无间,只是一理处”。⑤
延平对中和的解释亦是将理一分殊(体用)与中和未发已发相结合。他认为,从道的角度言,中和分指其体用;就人而言,则指未发已发。意味着道之体用与人之未发已发皆可以中和贯通起来,天人关系在中和那里得到协调统一。朱子称赞延平对此问题论述最详尽,当从体用来理解中和。“盖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则未发已发之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①朱子列举了延平几个重要说法。一是延平从《中庸》全书出发,确认未发之中是全书“指要”,可见未发之中的重要。“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②此较朱子《章句》所取龟山的首章为“一篇之体要”说更进一步。二是如何才是未发。延平说,“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③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人内心都会有无喜怒哀乐情感的时候,但这一无所喜怒哀乐之时并不等于未发之中,判定未发的标准不是外在情绪的宁静或波动,而是内心是否有主宰。未发之中实质是道德修养状态上升到相当高度才有的精神状态。外在情绪的发出与否只是一种表象,不能把表象当作实质。这一解释符合程门学派的精神,与朱子晚年对中和的理解一致。三是对“中和”具体字义、次序的理解。如延平把“致中和”的“致”解释为动态意义的努力、实现,符合《章句》“推而极之”的理解。在工夫次序上,延平明确提出中和境界必先经由慎独工夫方能实现。“又云致字如致师之致。又如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④须指出的是,以上对延平的反思回忆之说,符合朱子自身后来见解,但朱子明言当时并无此等领悟。此时他的看法是,认未发、大本为理一,已发、达用是分殊。延平纠正他将理一分殊与未发之说过于掺合的理解。如“太极动而生阳”朱子视为喜怒哀乐之已发,延平教导他这不是讲喜怒哀乐之发,而是阐发天人一理之同和人物分殊之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⑤
延平对朱子的影响还在于共同探讨二程、苏氏、吕大临、杨时等对《中庸》的解释,指导朱子收集诸家解说,扩大、加深对《中庸》的认识。作为道南学派的传人,延平师徒对杨时《中庸解》探讨最多。朱子后来在给林择之信中特别回忆龟山的中和说:“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①龟山的观点是未发体验中,已发获得和,以未发体验为工夫根本。朱子与此说不契,《中和旧说序》于此有深切追溯,“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②随延平探究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之说尚未领悟而先生已没,正是这种“未达”,促使朱子不断地进行探究。
四是延平非常注意纠正朱子的佛学倾向。如他批评朱子以“竿木随身”说解释《论语》“公山”章不合圣人气象,“竿木随身之说,气象不好,圣人定不如是。”③批评朱子对《中庸》“肫肫其仁”的解释,偏向佛学顿悟说,值得警惕。“大率论文字切在深潜缜密,然后蹊径不差。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恐其失处正坐此。不可不辨。”④批评朱子以孟子“必有事焉”一句解释“理一分殊”,有工夫落空陷入佛学之弊。“孟子之说,若以微言,恐下工夫处落空,如释氏然。”⑤针对朱子愧恨不能去心之弊,告之不可走向另一极端,“绝念不睬,以是为息念。”反复从“气象”上指出言辞有病,如“若常以不居其圣横在肚里,则非所以言圣人矣”“前后际断,使言语不著处不知不觉地流出来”等。延平对朱子的禅学底子有清醒认识,并不认为接触过佛学是坏事,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区分儒佛之异。他在《与罗博文》的信中说,“渠初从谦开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⑥
二儒佛之辨:辨张无垢《中庸解》
延平逝世后,朱子继续对《中庸》展开艰难探索,一个阶段总结性成果是在丙戌(1166年)冬撰写的《杂学辨》,该书分别批驳了《苏氏易学解》、《苏黄门老子解》、《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其中尤以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其实质是思想战线的一次交锋,通过划清儒与释老的界线,端正士子为学方向。故朱子特意挑选了在士子之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贵显名誉之士”,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士子会因崇拜名人而迷恋名人所崇拜的异端之学。“未论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选择张九成等名人加以批评体现了朱子的策略和勇气。朱子始终认为张九成佛学印迹特深,危害最大,“张公以佛语释儒书,其迹尤著。”九成与朱子所处时代最相近,对当时士子的影响最直接广泛;在学术渊源上与朱子又具有“血缘关系”,同出于龟山门下,与谢良佐亦有关联;且开启了此后朱子最大对手陆象山之学。对于这样一位“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释”的代表人物,朱子当然视为清理门户的首选了。朱子对无垢的著作有个基本判定,即“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效用之危害则是,“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故朱子毫不犹豫地亮出清理门户的卫道身份,以拯救世道人心,“尝欲为之论辨,以晓当世之惑”。朱子对张九成以禅解儒说的广为甚行极其担心,将其学说之流行喻为洪水猛兽。①无垢著作甚多,其佞佛最深者,则为《中庸解》,故朱子挑出全书五十二条予以批驳,“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②主要围绕性论、戒惧、忠恕、诚论、知行诸核心问题展开论辨,体现了朱子的佛学水平,反映出朱子此时中庸学的不成熟之处,显示出其对章句之学与辟佛老的一贯坚持,可谓早年学术之总结。
(一)性论:赞性、率性、觉性、见性
朱子对张氏性论的批评,针对其赞性、率性、觉性、见性说展开,体现了朱子此时对性的认识。“赞性”“体之为己物”。张氏认为天命之性说并没有对性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不过是称赞“性”之可贵,因其来源于天,是一普遍公共之状态,并未为人所个别拥有而“收为己物”。在率性之道时方才体性为自身之物,进入于五常之内。修道之教则表现为仁行于父子之类。“天命之谓性,第赞性之可贵耳,未见人收之为己物也。率性之谓道,则人体之为己物,而入于仁义礼智中矣……修道之谓教,则仁行于父子。”①朱子认为天命之性正是道出性之所以为性的本质所在,表明性是天赋人受,是义理之本原,非称赞性之可贵。并引董仲舒命为天令,性为生质说为证。反驳性“未为己物”说,既谓之“性”,则已经为人所禀赋了,否则无性可言。再则,性亦不存在待人“收为己物”。故张氏此说犯有两误。一方面人之生即同时禀赋天命之性,性与人俱生,否则人不成其为人矣。另一方面,性并非实存有形有方位之物,可收放储存,故以物言性不妥。“体之为己物”说亦不妥。性的内容乃是天赋之仁义礼智,并不需要待人去体验之,然后才入于五常之中。此皆不知为学大本妄加穿凿之病。再则仁行于父子等乃是率性之道而非修道之教,张氏颠倒道、教次序而不知。朱子晚年《章句》则从“理”立论,提出“性即理”说,强调性的普遍公共性,与此仅从人性上理解性不同。
“率性学者事,修教圣人功”。针对道、教关系,张氏作出两层区分:一是指圣人与学者的不同层次:率性是学者之事,以戒惧为工夫,修教则是圣人功用。修教之所以是圣人功用,是学者经由戒惧工夫而深入性之本原,达到天命在我境界后才能够发生的,以推行五常之教为主的效用。“方率性时,戒慎恐惧,此学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谓天命在我,然后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教,以幸于天下。”②朱子认为,率性之谓道是阐释道之为道的根据,意为遵循性之本然即是道,并非学者之事,亦不涉及戒惧之说。而修道为教是通贯上下的,贯穿了制定施为者圣人和修习者贤人。批评张氏直到深入性本原之说方才推行教的说法不合事理,将会导致遗弃伦理教化的后果,偏离儒家主旨,陷于释氏之说。“则是圣人未至此地之时,未有人伦之教……凡此皆烂漫无根之言,乃释氏之绪余,非吾儒之本指也。”二是指“离位”与否。朱子认为,率性并未离开性之本位,修道之教不可以“离位”来论,性不可以本位言,否则如物体一般有方位处所,“言性有本位,则性有方所矣”,与圣贤对性的超越说法相违背。再则无垢上章以“率性”为求中工夫,就“求”而言,则有离位之义。若非离位,何来求?
无垢认为,颜子由戒惧工夫,于喜怒哀乐之中悟未发已发之几,一旦获得天命之性善者,即深入其中,而忘掉人欲,丧失我心,达到一种无我无人,无欲无识的境界。“颜子戒慎恐惧,超然悟未发已发之几于喜怒哀乐处,一得天命之性所谓善者,则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丧。”还进一步提出,颜子拳拳服膺,实际已达到与天理为一,毫无私欲,人我皆忘的境地。所谓圣人,不过知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处,故当于此处求之。朱子指出《中庸》此处并无悟意,喜怒哀乐本即是性,中节即善,不存在得性与深入其善之说。否则,在此未悟之前,未得性而在性外乎?所谓“我心皆丧”说大大有害于理。张氏的“得性”说实际并非得到义,乃是领悟义。朱子为批评无垢,居然将“喜怒哀乐”之情直接等同于性,是非常罕见的(仅此一次)。尽管性由情显,但朱子成熟说法是喜怒哀乐是情,未发才是性,情有中节不中节之分,故不能直接说喜怒哀乐是性。
针对“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张氏提出人就是性,以人治人就是以我性觉彼性。“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觉彼之性。”①朱子指出,此非经文本意,乃释氏说。张氏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天命谓性,性无彼此之分,为天下公共之理,其理一也。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为人天生所固有,不存在得失假借之可能,故无法“以”之。张氏将见性与由乎中庸结合论述。“使其由此见性,则自然由乎中庸,而向来无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扫不见迹矣。”认为如有人能因他人之觉悟而见其本性,则自然能够实现中庸。而此前言行之无物无常,皆扫除无遗了无痕迹矣。朱子予以批驳:“愚谓‘见性’本释氏语,盖一见则已矣,儒者则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养而充之,以至于尽,其用力有渐,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际一有懈焉,则几微之间,所害多矣。”②指出见性本佛学术语,指证悟到佛性本空。儒者则言知性,由知性而进于存养扩充,以至于尽性。此本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儒佛之别在于:佛以见性为终极目的,见性之后更无余事。儒者则要历经由知性到尽性的长期充养扩充过程,需要在日用之间作持久的实践积累之功。佛学者虽有自命不凡,宣称见到性空者,但其人格修养、习气欲望则和常人一般,并未见其实有所得之处。张氏之说正是如此。张氏认为若诚呈现出来,则己性,以及人性、物性直至天地之性皆能呈现。朱子指出,《中庸》本言至诚尽性,而非诚见性见,“见”与“尽”意义大不相同。此不同正是儒佛所别:佛氏以见性为极致,而不知儒者尽性之广大。“见字与尽字意义逈别,大率释氏以见性成佛为极,而不知圣人尽性之大。”①
(二)戒慎恐惧:“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
张氏对戒慎恐惧极为重视,视为全篇枢纽,反复言说。仅就朱子所引52条来看,论及戒惧者即有17条之多,朱子对此痛加批评。张氏认为戒惧是未发以前工夫,使内心达到毫无私欲的状态。“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朱子则认为戒慎恐惧是已发,未发之前是天理浑然,“愚谓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②这和他以后的看法恰好颠倒,在中和之悟后他将戒慎恐惧当作未发,慎独当作已发。张氏进一步提出,通过戒慎恐惧工夫来存养喜怒哀乐之情感,以获得中和境界,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而朱子则从“本然、自然”的立场予以反驳,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乃是本然具有之中,发而中节,是其本然之和,中和是一本然状态而非人力所能为。天地位、万物育亦是理的自然发用。朱子此时承袭延平说,认为中和乃“一篇之指要”,晚年改变之,采用龟山全章乃一篇体要说。
以戒惧之说来贯穿《中庸》,实为张氏《中庸解》一大特色。在张氏看来,戒慎恐惧可解释《中庸》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如张氏认为“无忧者其惟文王”中“无忧”的原因在于:通过戒惧工夫达到无所不中和的境界;认为“博学者,戒慎恐惧,非一事也。”认为“大莫能载小莫能破”的原因在于“以其戒慎恐惧,察于微茫之功”也。朱子皆驳斥之,指出因张氏以戒惧一说横贯《中庸》全书,故屡屡造成牵合附会之病。“张氏戒慎恐惧二句,横贯《中庸》一篇之中,其牵合附会,连章累句,已不容一一辨正矣。”①张氏如此重视戒惧,用以解释全篇,是因为他认为中庸之道正是从戒惧工夫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君子自戒慎恐惧酝酿成中庸之道。”朱子批评“酝酿”不对,盖中庸之道乃天理自然,终始存在,并非因酝酿而产生。此批评亦未见得贴切,张氏酝酿与戒慎恐惧并列,指工夫之长久义,并非形容中庸之自然。
(三)辨忠恕:“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张氏对忠恕的阐发,遭到朱子最严厉批评,成为朱子最不能容忍的解释,认为其言“最害理”。他说: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责己也,知己之难克,然后知天下之未见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②
在忠、恕的界定上,张氏继承程门之说而又有重大偏离,其肯定恕来源于忠符合程门之义,但认为忠是责己、克己,恕是饶人、恕人之说则不合程门说。程子明确肯定“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故朱子肯定无垢“恕由忠生”说可取,但对“恕”的理解有很大问题。
愚谓恕由忠生,明道、谢子、侯子盖尝言之。然其为说,与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则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为义,本不如此。③
朱子解尽己为竭尽全部心力而毫无私意,推己则是在尽己基础上推扩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絜矩之道。张氏提出,一己之私难以克除,唯有见性者方能做到完全克除己私,明乎此,故对凡未能克除己私者、未能见性者皆加以宽恕,此即忠恕义。显然,张氏把忠理解为严以责己、恕为宽以待人。朱子批评张氏是以一己之私来对待天下之人。忠恕的本质是表现为如何对待人己关系,他引张载说指出应以责求他人之心来要求自己,以爱护自己之心来爱护别人。只有抱有责人以责己、爱己以爱人、众人以望人,才能做到人我之间心意相通、彼此一致,而各得其所、各守其则。朱子指出,如张氏之说,因己私难克而容忍他人私心之存在,以至于由此而发展为罪恶之事,其后果是诱导天下人皆流于禽兽境地,完全背离了儒家忠恕之教。朱子对张氏的忠恕批评一生保持未变,①并将张载的忠恕解写入《章句》。
朱子进而剖析张氏产生严重误解的原因在于章句文义理解的偏差。张氏主张此处断为四句,分别在“父”、“君”、“兄”、“之”后断。如张氏解,则理解为子父、臣君、兄弟、朋友之间的单边关系,即深入考察儿子侍奉父亲所应尽之道,而反思自身亦未能做到。因此,未敢要求父亲对儿子给予爱护之道。朱子指出张氏断句有误,“察”字理解有误。
愚谓此四句当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绝处,求犹责也,所责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则自有所未能。……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则安敢责父之爱子乎?”则是君臣父子漠然为路人矣。……盖其驰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详,故因以误为此说。②
此处当分为八句,应在子、臣、弟、友之后点断,这种断句的差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理解,朱子理解为子父、父子双边关系,即要求儿子对自己应做的,自己对父亲也没有做到,此时的“我”处于上下交错的人际关系中,“求”与“责”是同义(而非张氏的“察”)。当由张子《正蒙》“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说来自我劝勉,推扩,而并非如上章张氏所云“因为自身私意难以克除而容忍他人之私”,这样对私意的包容必然导致人心的堕落。张氏之误源于其深受佛学用心于空虚高明之所的影响,对文本章句未加详细审查。
“当于忠恕卜之”。张氏还提出,应当从是否做到忠恕来审察戒慎恐惧的效果,即戒惧为工夫,忠恕为效用;忠恕之效用又当自父母身上审察之。盖忠恕最切近者为事父母。“张云:欲知戒慎恐惧之效,当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当于父母卜之。”①朱子批评张氏之说牵强无理,视至尊的父母为卜算之物,其说已陷入“二本”而不知。张氏显然是比喻手法,朱子过于从字面理解。
(四)诚:无息为诚、知诚行诚、注诚于身
“认专为诚”与“无息为诚”。张氏指出学者多将“诚”误认为“专”,至诚本不息,若专则息矣。语言断绝,应对酬酢皆离开本位也。“世之论诚者多错认专为诚,夫至诚无息,专非诚也。以专为诚则是语言寝处,应对酬酢,皆离本位矣。”朱子予以反驳:“专”固然不足以表达“诚”之内涵,但如张氏以“无息”为诚,亦是错误。至诚之效用是不息,而非因无息方有诚之名义也。“离本位”亦非圣人说,乃是佛老之见。此意朱子始终未变,故《章句》言“诚故不息”。
此外,朱子还批评张氏“行诚不若知诚明,知诚不若行诚大”说,提出儒家思想中只有存诚、思诚,而无行诚说。通过思诚、存诚工夫,使诚内在于己,则其所行所发皆出于诚、合乎诚。而行诚说则把诚视为一个外在于己的事物看待,造成自我与诚的分裂,完全背离了诚之意义,后果极其严重。至于诵《孝经》御贼之说,其误在于事理不明而有迂腐愚蠢之弊,与诚无关。诵《仁王经》者,乃异端之见。
张氏关于诚的效用确有许多近乎佛老的过高之说。如他指出,注诚于身则诚,于亲则悦,于友则信,于君民则治。朱子指出,若能明善则自然诚身,此是理之自然。由身诚至于亲、友、君、民皆然,此是德盛自然所至。若言“注之而然”,则认为诚身与亲、友、君、民存在距离,尚须注入之过程,已陷入最大之不诚。再如“不诚无物”解为“吾诚一往,则耳目口鼻皆坏矣”说确实怪异。②朱子提出,诚不可以“吾”言,盖诚为本体,故不必言往。耳目口鼻,亦无一旦遽坏之理。
张氏认为,诚明谓之性,是指资质上等之人修道自得而合乎圣人教化;明诚谓之教,则是由遵从圣人教化以达到上智境界者。若有上智自得而不合乎圣人教化者,则为异端。朱子认为张氏对诚明理解的偏颇,适反映出其傲然自处于诚明之境,而实际陷于异端之学。此说的目的,是想通过“改头换面、阴予阳跻”的方式来达到掩盖其佛老之迹,避免别人怀疑的目的,此恰是其最大不诚之处。其实,张氏此说意在强调“合圣人之教”的重要性,以划清与佛老的界限,朱子的理解似乎有点“草木皆兵”之意味。
“变化天地皆在于我”。至诚无息章张氏提出天地之自章、自编、自成,其动力皆在于至诚不息之圣人,天地亦因此至诚不息而产生造化之妙用。朱子从文义与事理两面作出批驳:
张氏首要之误在于对本章文义理解有差,所谓不见、不动、无为皆是言至诚之理的效用,此理与天地之道相合。张氏则以为此言圣人至诚之效用,使天地彰明变化,不仅文义不通,且不合事理。而“天地自此造化”说更加危险奇怪,颠倒了圣人与天地上下关系,若如此说,则圣人反而造化天地,推测张氏说之蔽源于佛学“心法起灭天地”之说。①
(五)知论:“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
“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张氏指出,如果做到了智仁勇,则对九经无所期待用力而九经自然得到实行,一一合乎其道。“如其知仁勇,则亦不期于修身。”朱子指出此说会造成不良后果。若如张氏解,则九经皆为多余之说,张氏一心仰慕佛学高远虚灵之说而忽视了实地事为之功。
张氏指出,常人只是知道用知识去品评判断是非,而不知用之于戒惧恐惧工夫。若能“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方为大知。此说显然意在突出道德实践之知的优先性。朱子由此读出佛学的印迹,“故诠品是非,乃穷理之事,亦学者之急务也。岂释氏所称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遗意耶?呜呼,斯言也,其儒释所以分之始与!”朱子以穷理说批评张氏的移是非之心说,认为对事理是非的判断是天下正理,是一切知之开端,是人之本质和必须之当务,是行事合乎天理的必要前提。张氏完全忽视这一面,任其私知而不循天理,走向佛氏不问是非,仅求心证之途。讲求是非之知正可以作为判定儒释之分的第一标尺。有趣的是,朱子所引“直取无上菩提”与上文延平告诫朱子的“一超直入”说正好相应,可见朱子今非昔比。
张氏提出对格物的看法:“格物致知之学,内而一念,外而万事,无不穷其终始,穷而又穷,以至于极尽之地,人欲都尽,一旦廓然,则性善昭昭无可疑矣。”格物致知乃是从内外两面用功,包括内在意念与外在事物,皆要探究其终始,反复用功,达到人欲皆无的极致之地,此时心底廓然,唯有人性之善昭昭显露。由格物证悟到性善,使性善呈露彰显。朱子指出,格物当以二程之说为准,张氏之说乃是佛氏“看话头”的做法,背离了圣贤本旨,其病与吕本中《大学解》一致。
(六)章句工夫:“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
朱子在从学延平时即体现出好章句学的特点,给延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章句文义的辨析,亦淋漓尽致体现于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批评中。如前述对“所求乎子”一段的章句理解,朱子一生未能释怀,晚年还以此为典型批评以章句之学为陋的看法,提出“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的强势表述,突出了章句在义理理解中的优先性。这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章句之学于朱子而言,不是一般的文字解释,而是为学为道的工夫,是必要工夫,是首要、根本工夫。他说:
张子韶说《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点做一句。……而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贺孙。①
就短短五十二条《中庸解》来看,朱子多次指出张氏对文本的断句、字义理解有误,导致义理产生重大偏差。其中尤以“察”字的解释为有意味。除上引“所求乎子以事父”以“求”为“察”外,在“言顾行”的理解中,亦指出张氏将“顾”理解为“察”过于牵合,张氏所犯毛病在于就某一字义任意推衍,而不顾其是否合适可取。典型者如“戒慎恐惧”,忠恕、知仁勇、发育峻极等,张氏亦是将其贯穿全篇,任意使用。对费而隐章主旨的把握,“察”字亦很关键,朱子批评张氏把“上下察”的“察”解为“审察”不妥(朱子早年亦如此解),乃是“著察”义,如此才符合子思之义。张氏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已通过戒惧工夫开始致察,“察”无所不在。通过此“察”来养中和,在未发已发之间起为中和,使中和彰显之。朱子批评“起而为中和”说大悖理而不可理喻。
总之,朱子认为章句之学的疏略是导致张氏该书(学术)产生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特点的重要原因。朱子对张氏的评价是,“张氏之书,变怪惊眩盖不少矣。犹以为无有,不知更欲如何,乃为变怪惊眩哉。”①如张氏把“此天地之所以为大”释为由此可见夫子实未尝死,天地乃夫子之乾坤。朱子认为“不死之云,变怪骇人而实无余味。”②
三 阳儒阴佛思潮的“门户清理”
朱子在融汇前辈思想以建构理学学术大厦、构建理学道统之时,始终不忘“门户清理”工作,尤注意清理洛学内部阳儒阴佛思潮,认为洛学内部已经构成了一个“禅学化”集团,有其发展脉络和各阶段代表人物,危害极其之大。故该书看似针对张氏一人而发,其实具有普遍意义。
朱子以无垢为主线,清理出理学内部具有传承关系的“禅化”集团,其三个代表分别是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且愈往下其禅学程度愈深,表现愈明显,危害愈大。朱子指出上蔡入佛的表现主要在以知觉言仁,认为见心即仁,把心与仁直接等同起来,违背孔门之义,是由儒入佛的一大转向。其思想尽管隐秘,其源头乃分明是禅了。上蔡禅学程度尚轻,尚在儒学门户之内,不敢与儒学决裂。到了张九成,则又更进一步了。张氏亦主张以觉言仁,并变本加厉了。与谢氏不同,张九成有确切的佛学师承,拜师大慧宗杲,并深得其器重,因其气质豪雄粗疏,故与宗杲非常投缘。张氏大胆采用禅学,与儒家之说公然相冲突亦不顾,争夺门户,惑乱人心。张氏作为士人好佛的名士,树立了坏榜样,还把当时另一名士汪应辰引入佛门。集宋代士大夫佛学真正大成的则是陆九渊,其对儒学的背离又远在前人之上。朱子在未与陆氏兄弟(子寿、子静)见面前,便风闻二兄弟学宗张氏①,内心颇为不安。越到晚年,尤其是与陆氏学术对立日益明显之后,就越加笃定金溪之学就是禅学,是真正的禅学,并根据自身学佛经验现身说法,指出张拭、吕祖谦因未学佛的缘故,未能看出陆氏之学的要害,其实只要看看相关佛经如《楞严》等,陆氏佛学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陆氏之天分、口才,影响皆较前者远甚,且与朱子同时,故成为朱子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病。
(盖卿录云:孔门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一转云云)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张子韶出来,尽冲突了。近年陆子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方子。②
又说张无垢参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后来亦好佛。③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④
朱子选择张九成作为突破口,试图端正“禅者之经”的学术倾向,用心良苦。张九成人品高洁伟岸,学有渊源,曾问学于杨龟山,是二程学派的传人,为南宋初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⑤且张氏“以禅解经”的著作当时很受欢迎。朱子非常警惕“内部人士”“禅者解经”的佛化倾向,它表明佛学思想对儒家侵蚀极深,危害极大。故直接将张氏说判为“洪水猛兽”,以突出其对学者心灵的巨大负面作用。朱子视张氏为“禅者解经”的代表,这种“禅者”不是信佛僧人,而是佛化的儒家学者。“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①朱子对张氏“可怪”之说一向秉持拒斥、消除态度。对其著作在浙江之刊行数次极表忧虑,盖其著作是“坏人心之甚者”,深惧其贻害无穷。并由此反思自身当加强对儒学的研讨,以救其祸害。
近闻越州洪适,欲刊张子韶经解,为之忧叹不能去怀。②
闻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学浅,又未有以遏之。③
比见婺中所刻无垢《日新》之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无力可救,但窃恐惧而已。④
朱子发明“无垢句法”一词来概括张氏以禅解儒、凭空杜撰、“脱空狂妄”、肆意想象、无济于事的解经风格。⑤“无垢句法”作为一专有名词,朱子常用以警示弟子。指出这种错误不仅是文义理解问题,且关乎思想的根本走向,是不可容忍,必须改正的。由此形成一种“辟无垢”的氛围。如批评林择之“同一机者”之说“颇类无垢句法”。⑥且朱子弟子中确有张氏的崇拜者,他们甚至不满于朱子对张氏的批评,尤其在早期弟子中。如许顺之即是如此。朱子在给许氏的信中要求他以张氏之学为戒而不是为学。“如子韶之说,直截不是正理……此可以为戒而不可学也。”⑦即便对得意高弟如吴伯丰、陈淳,只要解释稍有过高之处,朱子即以“无垢句法”告之。“此段大支蔓,语气颇似张无垢,更宜收敛。”①对于初次来学者,朱子则会了解其学术背景,主动询问是否受过张氏影响,可见朱子对此之重视,这与朱子关注问学者是否从学金溪相似。如窦从周初见朱子时,曾问起之。“问曾看无垢文字否?某说亦曾看。问如何?”从周。②
朱子对无垢以禅解经的实际案例时刻注意抨击。如指出其解释孟子四端说“犹是禅学意思,只要想象。”对其《论语》评论较多,指出多有与上蔡相同处,如有学者问,“张子韶有一片论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说亦然。”大雅。③朱子指出张氏认为佛氏有形而上而无形而下之说非常可笑,割裂了道之体用。“顷见苏子由、张子韶书,皆以佛学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尝窃笑之。”④特别是批评张氏“事亲体认”说陷入“二心”说,实为禅学之当机认取,使事亲事兄的意义工具化,仅成为体认仁的手段。
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僴。⑤
总之,朱子对张九成《中庸解》的辨析紧紧围绕文本字义与义理解析展开,尤为注重揭示《中庸解》的佛老因素。朱子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对文义的把握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章句文字之学,而是把握思想义理的首要之关。无论是思想的正面建构还是反面批驳,皆须先从文义入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朱子的为学工夫中,章句之学是其首要之门,与西方逻辑分析之学亦有相通之处,故应提高对其意义与价值的重视。对张九成的批判亦集中展现了朱子从学延平后这一时期的《中庸》水平,显示了与其后期成熟思想的延续性和差异性,真实记录了朱子思想发展的阶段特质,堪称朱子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朱子在辨析中熟练运用大量佛学术语批判对方,体现了朱子对佛学的认知掌握,显示出对佛学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思想自信。可见,辟除理学内部“禅者解经”的清理门户工作,与吸收前辈思想开展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于朱子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附注
①《语类》卷12,第367页。
②《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7页。
①《四书集注》,第195页。
②《语类》卷78,第2671—2672页。
①《答陈同甫》六,《文集》卷36,第1583页。
②《答陈同甫》八,《文集》卷36,第1588页。
③陈荣捷:《新道统》,《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④乾道壬辰年给石子重写的《克斋记》中,朱子在阐述完对仁的看法后,即提到“然自圣贤既远,此学不传,及程氏两先生出,而后学者始得复闻其说,顾有志焉者或寡矣。”《文集》第3710页。可见,朱子此时对道统大体已经有初步看法,此学理解为“仁学”亦无不可。
①《语类》卷78,第2671页。
①《语类》卷78,第2671页。
②同上书,第2674页。
③《语类》卷13,第389页。
①《语类》卷62,第2013页。
②《语类》卷78,第2667页。
③《文集》卷56,第2680页。
④《语类》卷62,第2012页。
①《语类》卷62,第2012页。
②《语类》卷78,第2668页。
③《语类》卷62,第2014—2015页。
④《语类》卷78,第2667页。
⑤同上书,第2673页。
①《语类》卷78,第2666页。
②《语类》卷62,第2014页。
①《语类》卷78,第2670页。
②同上书,第2667页。《语类》表明郑可学所记通常为辛亥,似当在戊申,论证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③张洽所录有丁未1187、癸丑1193两个年代,此据前后《语类》当为后者,《语类》卷78,第2668—2669页。
④《语类》卷78,第2663页。
⑤同上书,第2663—2664页。
⑥《语类》卷13,第389页。
①《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4页。
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③同上书,第123页。
④同上书,第256页。
⑤同上书,第312页。
①与朱子相反,阳明赞同程子说,认为伊川人心人欲说是心欲一体说,朱子道心主宰人心反倒过于分析,是二心说。“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②《语类》卷78,第2664页。
①《语类》卷13,第389页。
①《语类》卷78,第2665页。
②《语类》卷13,第388页。
③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83页。
①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84页。
①《语类》卷78,第2671页。
②同上书,第2671页
③同上书,第2673页。
①《壬午应诏封事》,《文集》卷11,第573页。
②《观心说》,《文集》卷67,第3278页。
③《答詹帅书》,《文集》卷27,第1205页。
①陈逢源:《朱熹论道统——重论朱熹四书编次》,《东华汉学》2005年第3期。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页。
①钱穆:《朱子论人心与道心》,载《朱子新学案》第2册,第201页。
②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25页。
③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6页。
①《戊申封事》,《文集》卷11,第591页。
②《文集》卷14,第664页。
①《文集》卷74,第3590页。
②《语类》卷41,第1467页。吕焘己未1199年所闻。
①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0页。
①《语类》卷41,第1462页。
②《文集》卷77,第3709。
③《语类》卷45,第1587页。
④《语类》卷124,第3891页。
①《语类》卷27,第982—983页。
②《语类》卷104,第3437页。
③《语类》卷124,第3881页。
④同上书,第3880页。
①《朱先生行状》,载《朱子全书》,第27册,第566页。如黄榦《朱子行状》称儒家道统“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按:《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05页。有缺漏误“孟子”为“孔子”。陈淳《严陵讲义·师友渊源》认为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页。
②《答廖子晦》十六,《文集》卷45,第2108页。
③朱熹:《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①张栻:《南轩集》卷20,《四库全书》1167册,第588页。
②吕祖谦:《东莱别集》卷7,第399页。
③《答杨子直》,《文集》卷45,第2075页。
①胡炳文:《四书通·论语通》卷3,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132页。
①赵刚:《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②向世陵:《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
③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67页。
①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第六章“学派的自我定位”,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03年版,第269—295页。
②吴震:《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①朱公迁:《四书通旨》卷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7页。
①《语类》卷27,第965页。
②《答虞士朋》,《文集》卷45,第2059页。
③《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
①关于理和一的具体所指,陈来先生认为应根据具体语境做出有针对性的分析,“理一分殊这一命题在朱熹哲学中含有多种意义,实际上被朱熹作为一个模式处理各种跟本原与派生、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别有关的问题。”《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版,第123页。
②《语类》卷27,第984页。
③《语类》卷21,第723页。
①《语类》卷27,第999页。
②《语类》卷27,第995页。
③同上书,第967页。
④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本书所引《四书或问》皆为此版本。
⑤《语类》卷27,第992页。
①《语类》卷27,第993页。
②《语类》卷27,第968页。
③同上书,第976—977页。
④同上书,第990页。
①《语类》卷27,第966页。
②同上书,第969页。
③《语类》卷27,第979—980页。
④《文集》卷60,第2894页。
⑤《语类》卷27,第996页。
⑥同上书,第966页。
①《语类》卷27,第972页。
②同上书,第975页。
③《语类》卷27,第970页。
④同上。
⑤同上书,第985页。
①《语类》卷45,第1584页。
①《语类》卷27,第976页。
②同上书,第969页。
③同上书,第997页。
①《语类》卷27,第972页。
②《语类》卷21,第730页。
③《语类》卷27,第997页。
④同上书,第969页。
⑤同上书,第996页。
⑥同上书,第987页。
⑦《语类》卷45,第1585页。
①《语类》卷27,第1003页。
②同上书,第980—981页。
③同上书,第982—983页。
④《语类》卷27,第982页。
⑤同上书,第974页。
①《语类》卷27,第1003页。
②同上。
①《语类》卷27,第999页。朱子此时主要讨论对象是范直阁、胡籍溪、吴耕老等,他在戊寅年和范直阁有四封信集中讨论忠恕说(见《与范直阁》,《文集》卷37)充分反映出朱熹早期对忠恕之看法。
②甲申1164年,《答柯国材》四,《文集》卷39,第1732页。程、谢之说皆发挥了忠恕之本末、天道人道、体用关系义,见朱熹《论孟精义·论语精义》二下,《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③甲午1174,《答吕子约》十,《文集》卷47,第2183页。
①乙卯1195年,《答曾无疑》五,《文集》卷60,第2891—2892页。
②《语类》卷27,第1001—1002页。
③同上书,第1002页。
①《语类》卷27,第1000页。
②《论孟精义·论语精义》,第155页。
③《语类》卷27,第1002页。
①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6页。
①学界近年对道统研究颇多,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对整个道统史的研究,如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苏费翔、田浩著、肖永明译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中华书局2018年版);二是对朱子之前重要人物道统思想的研究,如孟子、韩愈等道统思想;三是对朱子之后心学道统的研究,如陈畅《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吴震《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四是对儒家道统提出新说,如牟宗三先生的理学三系,判朱子“别子为宗”说,又如梁涛先生《儒家道统说新探》纳荀子于道统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五是关于朱子道统的研究,各类著作都会涉及,影响较大的是陈荣捷、余英时两位先生具有差异性的研究等。另外专论朱子道统的论文有数十篇之多,较侧重从《中庸章句》、《尚书》“十六字心传”入手,亦有少量从易学角度论证者。而在朱子道统中比较困惑的周、程关系上,迄今仍无较合理的解释出现。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卷30对儒学的概述亦是据经典(六经)、概念(仁义)、人物(尧舜文武仲尼)三个方面,言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本文侧重从学统、道学的角度论述道统,亦可谓狭义的道统观,近乎陈荣捷先生;而不同于通贯学统、政统的道统观,如余英时、陈畅等。
②仅从词源的意义上,是否朱子首先使用“道统”一词,学界近来有不同看法。我想,从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来论述“道统”,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范畴,始于朱子应是无疑的。此外,学者对“道统”看法亦不一,如唐宇元认为道统是“一种把握儒家的原则、尺度。”《道统抉微》,《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陈来先生认为今天理解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蔡方鹿先生认为,道统就是道的传授统绪。详见蔡方鹿《文化传承与道统重构》,《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8日。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④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江求流认为“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本意相去甚远”。见《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2期。
②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0页。元儒许谦《读四书丛说》提出“统”专指掌握政治权力的君王,“学”则涵摄“统”,兼顾有位无位者。此说不合朱子意。“道学主于学,兼上下言之。道统主于行,独以有位者言之。……凡言统者,学亦在其中。学字固可包括统字。”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二,《四库全书》第202册,第558页。
③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2页。
④同上书,第14页。
⑤《文集》卷36,第1576页。
⑥《文集》卷61,第2974页。
⑦《语类》卷13,第408页。
⑧《语类》卷19,第652页。
①《文集》卷86,第4050页。
②学者对此有所论证,赖区平:《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1期。陈来先生认为二者关系如果加以区分的话:“道统是道的传承谱系,道学是道的传承内容。”《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并指出余英时之道统与道学之辨另有用意。蔡方鹿先生认为道统与道学是一体两面,分指形式与内容。《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③《语类》卷62,第2051页。
④《四书集注》“道学”作为专名出现了三次,见出道学与道统的包涵性。《中庸章句序》开篇言“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也”;《论语集注》“子曰管仲之器小”章引杨时说“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兴于诗”章注:“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⑤谢晓东:《寻求真理:朱子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探索》,《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①《文集》卷75,第3639页。
②方旭东对此有详细论述,认为“在评价朱熹道学观时,我们对《近思录》的史料价值应有清醒的估计”。《〈近思录〉新论》,《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③绍熙癸丑(1193)《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文集》卷80,第3803页。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7页。
②邓庆平:《周必大对道学学派的批评》,《孔子研究》2014年第6期。
①《语类》卷14,第419页。
②同上书,第430页。
③《语类》卷19,第645页。
④《语类》卷105,第3450页。
①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第九章《朱熹的〈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①《语类》卷12,第371页。
②同上书,第366页。
③同上书,第367页。
④同上书,第371页。
⑤《语类》卷18,第634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②《语类》卷15,第490页。
③同上书,第480—481页。
④同上书,第481页。
⑤《四书集注》,第3页。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第289页。
②陈荣捷:《朱学论集》,第15页。
③同上书,第17页。
④有学者视朱子此不同说法为“文体差异”或说法无定,如苏费翔认为此说明“朱熹道统的用词终身还没有定下来”。(《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粟品孝《周敦颐学术史地位的建构历程》亦认为朱熹对道统的看法具有不稳定性。
⑤程颢、程颐:《二程外书》卷12,《二程集》,第424页。
⑥元儒胡炳文据孟子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之分,故《集注》仅提及二程传道与《文集》赞濂溪觉道说并不矛盾,濂溪对道之体悟是闻而知之,二程乃是见而知之。孟子强调闻知、见知意在突出明道的重要。“今言明道而不言濓溪者,二程夫子受学于濓溪先生,见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圣之相传者,非徒为其行道而言,实为其闻知、见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四书通·孟子通》卷14,第588页。业师李景林先生亦注意区分二者之别,指出:“这‘闻而知之’者一类,大体上都是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一种新时代或文明新局面的开创者;‘见而知之’者一类人,则基本上属于儒家所说的贤人或智者,是一种既成事业的继承者。”《论孟子的道统与学统意识》,《湖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①《文集》卷78,第3740页。
②同上书,第3743页。
③同上书,第3748页。
④《文集》卷79,第3760—3761页。
⑤同上书,第3768—3769页。
⑥《文集》卷80,第3803页。
①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认可与否定周程关系的双方各有证据。但总体来看,反方证据来自二程,更直接可靠,个人以为,濂溪思想中较为浓重的道家归隐无为思想与二程思想旨趣颇为不类。尽管普遍认为濂溪开启了二程“寻孔颜乐处”,但二程对此命题的理解与濂溪或许存在不少差异。
②李存山:《〈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①有学者提出“大易道统论”。张克宾:《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周易研究》2012年第5期。王风:《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与易学之关系》纯以伏羲易论朱子道统,《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②《文集》卷36,第1567页。
③《文集》卷46,第2155页。
④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00页。
⑤《语类》卷94,第3122页。
⑥同上。
①《语类》卷59,第1888页。
②朱子对君王的要求,则提“皇极”,并将“大中”解为“此是圣王正身以作民之准则”,《语类》卷79,第2710页。余英时、吴震先生从政治的角度解释朱子“皇极”说,陈来先生则认为朱子仍然主要就经典解释而论皇极,其时事意味只是连带论及而已。参见吴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复旦学报》2012年第6期;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①《语类》卷6,第240页。
①《文集》卷30,第1306页。
②《语类》卷94,第3153页。
③《语类》卷94,第3144页。
④同上书,第3144页。
①此二条为吕祖谦主张选入,朱子初虽反对,后亦觉得可存。《答吕伯恭》言“但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者),今看得似不可无。”《文集》卷33,第1460页。
②《答张元德》,《文集》卷62,第2981页。
①《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982页。
②《语类》卷59,第1888页。
③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以下简称《勉斋文集》)卷26,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4页。
①黄榦:《勉斋文集》卷34,第701页。
①张克宾:《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周易研究》2012年第5期。
②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第154页。
③同上书,第148—154页。
④《语类》卷130,第3421页。
①《延平答问》,《朱子全书》十三册,第351页。
②《答何叔京》,《文集》卷40,第1802页。
①《语类》卷130,第3416页。
②《延平答问·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第354页。
③《延平答问》,第335页。
④同上书,第330页。
⑤同上书,第337页。
①《答林择之》,《文集》卷43,第1979页。
②《延平答问》,第351页。
③《答林择之》,《文集》卷43,第1979—1980页。
④同上书,第1980页。
⑤《延平答问》,第329页。
①《答林择之》,《文集》卷43,第1979页。
②《文集》卷75,第3634页。
③《延平答问》,第327页。
④同上书,第331页。
⑤同上书,第335—336页。
⑥李侗:《李延平集》卷1,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页。
①“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文集》卷42,《答石子重》五,第1924页。
②《张无垢中庸解》,《文集》卷72,第3473页。
①《张无垢中庸解》,《文集》卷72,第3473—3474页。
②《张无垢中庸解》,第3475页。
①《张无垢中庸解》,第3478页。
②同上书,第3478—3479页。
①《张无垢中庸解》,第3488页。
②同上书,第3475页。
①《张无垢中庸解》,第3491页。
②《张无垢中庸解》,第3479页。
③同上。
①在《中庸或问》中,朱子继续批评张氏忠恕说,认为此说后果极其严重,“此非所谓将使天下皆无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于是乎验矣”。《四书或问》,第577页。《语类》亦以张氏说为反面典型。张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我不会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则相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语类》卷42,第1485页)
②《张无垢中庸解》,第3480页。
①《张无垢中庸解》,第3481页。
②《张无垢中庸解》,第3489页。
①张载言:“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欤?”《张载集·大心篇》,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6页。
①《语类》卷56,第1814页。
①《张无垢中庸解》,第3490页。
②《张无垢中庸解》,第3491页。
①“陆子寿闻其名甚久,恨未识之。子澄云其议论颇宗无垢。不知今竟如何也?”《答吕伯恭》,《文集》卷33,第1445页。
②《语类》卷20,第707页。“问:张无垢说仁者,觉也。”贺孙。《语类》卷20,第690页。又曰:“上蔡多说知觉,自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学蒙。《语类》卷123,第3867页。
③《语类》卷126,第3959页。
④《语类》卷124,第3882页。
⑤朱子认为张氏虽名出龟山门下,实则与龟山不同。相反,却将其与上蔡视为一路,值得玩味。“至于张子韶、喻子才之徒,虽云亲见龟山,然其言论风旨,规摹气象,自与龟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盖尝深辟之。”(《文集》卷41,《答程允夫》,第1873—1874页。)如朱子亦称“张子韶人物甚伟”。(《语类》卷127,第3985页。)全祖望亦认为:“龟山弟子以风节光显者,无如横浦,而驳学亦以横浦为最。”(《宋元学案·序录》)
①《语类》卷11,第351—352页。
②《答许顺之》,《文集》卷39,第1748页。
③《答石子重》,《文集》卷42,第1924页。
④《答吕伯恭》,《文集》卷33,第1424页。
⑤“今人有一等杜撰学问,皆是脱空狂妄,不济一钱事。如‘天下归仁’只管自说‘天下归仁’……到念虑起处,却又是非礼,此皆是妄论。子韶之学正如此。”履孙。《语类》卷58,第1857—1858页。
⑥《答林择之》,《文集》卷43,第1977页。
⑦《答许顺之》,《文集》卷39,第1737页。
①《答陈安卿》,《文集》卷57,第2721页。
②《语类》卷78,第2673页。
③《语类》卷29,第1063页。
④《答韩无咎》,《文集》卷37,第1623页。
⑤《语类》卷35,第1303—1304页。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