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复礼”即“复天理之节文”
| 内容出处: |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640 |
| 颗粒名称: | 五、“复礼”即“复天理之节文”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7 |
| 页码: | 134-14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强调“礼”的根源是“天理”,而“节文”是“天理”的表现形式。本文从朱熹对“礼”的诠释入手,探讨了他如何将“天理”和“节文”结合起来诠释“礼”,并指出这种诠释的理学理路。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朱熹释“礼”为“天理之节文”的实质,并探讨了这种诠释对于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意义。 |
| 关键词: | 朱熹 克己复礼 哲学思想 |
内容
朱熹释“礼”为“天理”,把形而下的“礼”上升为形而上的“天理”;又常释“礼”为“节文”,强调礼的规矩准绳义。以“天理”释“礼”,旨意高远,很难显示“礼”的精微缜密;以“节文”释“礼”,溺于卑近,虽能体现其对形下践履之“礼”的重视,但无法兼顾“礼”蕴含的形上超越之“理”。既然释“礼”时,“天理”为必要,“节文”又必不可少,那么,在朱熹诠释《论语》“礼”的过程中,是否有两全之释,能同时兼顾形而上之“天理”和形而下之“节文”呢?细研文本,在朱熹的经典诠释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两全之释: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即理之节文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礼,谓义理之节文。②
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人之所当行者。……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①
在上述引文中,朱熹直接将“天理”(“理”“义理”)与“节文”并举,以前者修饰、限定后者,形成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其中以“礼者,天理之节文也”最为典型。那么,这个短语的具体意涵又该如何理解?朱熹兼顾形上、形下两个层面诠释“礼”的理学理路何在?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方面,“天理”是根源,“节文”是表现,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是当然之理的自然生发。
朱熹释“礼”为“天理之节文”,始终认为“天理”是礼之根源,“节文”是“天理”的具体表现。《朱子语类》记载,朱熹68岁时对此有明确论述:
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节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节文;夫妇长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实皆天理也。②
这段话首尾两端皆立足于“天理”。在朱熹看来,天下皆有“当然之理”,“复礼”首先是“复天理”,但“天理”无形无影,“节文”就是圣贤画出来的可供人看、可供人凭据的“天理”,“天理”是当然的、超越的,是根源和归旨,“节文”是“天理”的形式具现,“礼”就是呈现当然之“天理”的可做规矩凭依的“节文”。
朱熹在晚年67岁后曾与学生就“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展开讨论:
吴(伯游)问“礼之用,和为贵”。先生令坐中各说所见。铢曰:“顷以先生所教思之: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人之所当行者。人若知得是合当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讨一个和来添也。”曰:“人须是穷理,见得这个道理合当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门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为此,终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灯花落手,便须说痛。到灼艾时,因甚不以为苦?缘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于情愿,自不以为痛也。”①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自然“合当用恁地”,人只有事先穷理,知道道理应当如此,才会心甘情愿地、自主地施行相应的“节文”,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入公门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等礼节才会恰到好处地落实,否则,如果不明晓天理,礼之节文就很难做到。朱熹还通过对比个体面对“灯花落手”与“灼艾”两种疼痛的不同反应和态度来告诉我们,“合当用恁地”“天理”是“节文”表现的内在根据,只要内心“出于情愿”,即便是痛也不痛了。
朱熹61岁后还指出:
前日戏与赵之钦说,须画一个圈子,就中更画大小次第作圈。中间圈子写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写“仁义礼智”四字。“仁”之下写“恻隐”,“恻隐”下写“事亲”,“事亲”下写“仁民”,“仁民”下写“爱物”。……于“礼”下写“辞逊”,“辞逊”下写“节文”。②
推究朱熹所画圈子的层级,结合其视“礼”为“性”,发展“性即理”学说,可见,此处作为本有之性的“礼”与“理”同,“礼”与“节文”、“天理”与“节文”显然不属于同一层级,“节文”是礼(理)之由内向外的自然推扩,“天理”规范着“节文”,是内在之根本,“天理”藉由“节文”彰显,“节文”是“天理”的外在表现。
《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先后于64岁、70岁时曾从反面来讨论“天理”是礼之根源、“节文”是外在表现:
问:“……若天理不亡,则见得礼乐本意,皆是天理中发出来,自然有序而和。若是胸中不有正理,虽周旋于礼乐之间,但见得私意扰扰,所谓升降揖逊,铿锵节奏,为何等物!不是礼乐无序与不和,是他自见得无序与不和,而礼乐之理只在也。”曰:“只是如此。”①
问:“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着,若无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
以朱熹之见,若心中无这“天理”,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等“节文”动作皆为空有,不能算作真正的礼乐。“天理”为根本,周旋百拜等礼之仪节是“天理”的表现形式。在第一段对话中,虽然朱熹的回答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提问的学生皆视“天理”为礼乐之根源,皆认为礼乐是从“天理”中生发出来,若无这“天理”,升降揖逊、铿锵节奏等皆无法成为礼乐。
另一方面,“天理”是体,“节文”是用,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兼备体用。
就体用而言,朱熹视“天理”为体、“节文”为用、“礼”兼体用。
朱熹在礼是性、性即理、礼即理的诠释转换中释“天理”为形而上之体。“仁义礼智,性也,体也”②;“仁义礼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岂可分也”③;“性,即理也”④。在朱熹看来,“礼”“性”“理”“体”等是可以依次推导的概念,因而“理”即“体”。对此,朱熹还从另一个视角来予以论证。在回答杨至之问“体”时,朱熹明确指出:“合当底是体。”⑤他又曾指出:“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①朱熹认为“合当底是体”,而作为“天理”之“礼”为“天下当然之理”,是“合当恁地”,自然为“体”。
朱熹释“节文”为形而下之用,为“事宜”。其70岁所作《答曾择之》言:
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见其大概之所宜,然到礼上方见其威仪法则之详也。节文仪则,是曰事宜。②
朱熹在诠释《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之“礼”时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③这较之“礼者,天理之节文”更为周匝。《答曾择之》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朱熹认为,“天理”是形而上、无形无迹的“理”,“节文”(“品节文章”)是形而下、可见可行的“事宜”。“天理”和“节文”的关系即为“理”“事”的关系。“天理之节文”和“人事之仪则”虽是两个层次的说明,其本质皆指出“理(天理)”为体,“事(节文)”为用。对此,朱熹的得意门生陈淳亦有颇为恰当的阐释:
文公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以两句对言之,何也?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见于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其体而人事其用也。“仪”谓容仪而形见于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与“文”字相应。“则”谓法则、准则,是个骨子,所以存于中者,乃确然不易之意,与“节”字相应。文而后仪,节而后则,必有天理之节文而后有人事之仪则。言须尽此二者,意乃圆备。④
陈淳认为,“天理之节文”与“人事之仪则”是相对而言的,“天理”在中,对应“人事”在外,“节”“则”在中,对应“文”“仪”在外,“天理其体”对应“人事其用”,而“节文”为“事宜”;天理为“体”,相应的,作为“事宜”之“节文”自然为用。这是深得朱熹本意的。
朱熹视“天理”为体、“节文”为用,以体之“天理”和用之“节文”并释“礼”,意在突出“礼”兼备体用,这正是朱熹“礼”之释的高明之处。《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有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
人只是合当做底便是体,人做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如尺与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铢,则体也;将去秤量物事,则用也。①
朱熹持“礼”之体用兼备观,明确批驳“公江西有般乡谈”,意在反对“江西”陆学之认虚空者为体,好比尺无寸、秤无星,自然无尺秤之用。朱熹认为,按照天理、规矩去做,就是礼之体,这里强调的是做的“合当”性,不强调做本身,因为做本身(“做处”)就是用,如此一来,作为“合当做”的礼就同时具备体和用,就如体用兼备的扇子,柄、骨子、纸糊等是体,“人摇之”是用,两者绝不能截然分开。与此类似的论述还出现在朱熹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如其《答赵致道》言:
不曰理而曰礼者,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故圣人之言体用兼该、本末一贯。②
总而言之,朱熹释“礼”为“天理之节文”,兼备体用,一方面体现出其形而上的“天理”之“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兼顾其形而下的“节文”之“用”的特征,对“礼”的体用做了充分展示,凸显了他倡导的“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①的学术旨趣。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即理之节文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礼,谓义理之节文。②
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人之所当行者。……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①
在上述引文中,朱熹直接将“天理”(“理”“义理”)与“节文”并举,以前者修饰、限定后者,形成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其中以“礼者,天理之节文也”最为典型。那么,这个短语的具体意涵又该如何理解?朱熹兼顾形上、形下两个层面诠释“礼”的理学理路何在?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方面,“天理”是根源,“节文”是表现,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是当然之理的自然生发。
朱熹释“礼”为“天理之节文”,始终认为“天理”是礼之根源,“节文”是“天理”的具体表现。《朱子语类》记载,朱熹68岁时对此有明确论述:
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节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节文;夫妇长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实皆天理也。②
这段话首尾两端皆立足于“天理”。在朱熹看来,天下皆有“当然之理”,“复礼”首先是“复天理”,但“天理”无形无影,“节文”就是圣贤画出来的可供人看、可供人凭据的“天理”,“天理”是当然的、超越的,是根源和归旨,“节文”是“天理”的形式具现,“礼”就是呈现当然之“天理”的可做规矩凭依的“节文”。
朱熹在晚年67岁后曾与学生就“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展开讨论:
吴(伯游)问“礼之用,和为贵”。先生令坐中各说所见。铢曰:“顷以先生所教思之:礼者,天理节文之自然,人之所当行者。人若知得是合当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讨一个和来添也。”曰:“人须是穷理,见得这个道理合当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门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为此,终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灯花落手,便须说痛。到灼艾时,因甚不以为苦?缘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于情愿,自不以为痛也。”①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自然“合当用恁地”,人只有事先穷理,知道道理应当如此,才会心甘情愿地、自主地施行相应的“节文”,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入公门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等礼节才会恰到好处地落实,否则,如果不明晓天理,礼之节文就很难做到。朱熹还通过对比个体面对“灯花落手”与“灼艾”两种疼痛的不同反应和态度来告诉我们,“合当用恁地”“天理”是“节文”表现的内在根据,只要内心“出于情愿”,即便是痛也不痛了。
朱熹61岁后还指出:
前日戏与赵之钦说,须画一个圈子,就中更画大小次第作圈。中间圈子写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写“仁义礼智”四字。“仁”之下写“恻隐”,“恻隐”下写“事亲”,“事亲”下写“仁民”,“仁民”下写“爱物”。……于“礼”下写“辞逊”,“辞逊”下写“节文”。②
推究朱熹所画圈子的层级,结合其视“礼”为“性”,发展“性即理”学说,可见,此处作为本有之性的“礼”与“理”同,“礼”与“节文”、“天理”与“节文”显然不属于同一层级,“节文”是礼(理)之由内向外的自然推扩,“天理”规范着“节文”,是内在之根本,“天理”藉由“节文”彰显,“节文”是“天理”的外在表现。
《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先后于64岁、70岁时曾从反面来讨论“天理”是礼之根源、“节文”是外在表现:
问:“……若天理不亡,则见得礼乐本意,皆是天理中发出来,自然有序而和。若是胸中不有正理,虽周旋于礼乐之间,但见得私意扰扰,所谓升降揖逊,铿锵节奏,为何等物!不是礼乐无序与不和,是他自见得无序与不和,而礼乐之理只在也。”曰:“只是如此。”①
问:“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着,若无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
以朱熹之见,若心中无这“天理”,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等“节文”动作皆为空有,不能算作真正的礼乐。“天理”为根本,周旋百拜等礼之仪节是“天理”的表现形式。在第一段对话中,虽然朱熹的回答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提问的学生皆视“天理”为礼乐之根源,皆认为礼乐是从“天理”中生发出来,若无这“天理”,升降揖逊、铿锵节奏等皆无法成为礼乐。
另一方面,“天理”是体,“节文”是用,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兼备体用。
就体用而言,朱熹视“天理”为体、“节文”为用、“礼”兼体用。
朱熹在礼是性、性即理、礼即理的诠释转换中释“天理”为形而上之体。“仁义礼智,性也,体也”②;“仁义礼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岂可分也”③;“性,即理也”④。在朱熹看来,“礼”“性”“理”“体”等是可以依次推导的概念,因而“理”即“体”。对此,朱熹还从另一个视角来予以论证。在回答杨至之问“体”时,朱熹明确指出:“合当底是体。”⑤他又曾指出:“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①朱熹认为“合当底是体”,而作为“天理”之“礼”为“天下当然之理”,是“合当恁地”,自然为“体”。
朱熹释“节文”为形而下之用,为“事宜”。其70岁所作《答曾择之》言:
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见其大概之所宜,然到礼上方见其威仪法则之详也。节文仪则,是曰事宜。②
朱熹在诠释《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之“礼”时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③这较之“礼者,天理之节文”更为周匝。《答曾择之》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朱熹认为,“天理”是形而上、无形无迹的“理”,“节文”(“品节文章”)是形而下、可见可行的“事宜”。“天理”和“节文”的关系即为“理”“事”的关系。“天理之节文”和“人事之仪则”虽是两个层次的说明,其本质皆指出“理(天理)”为体,“事(节文)”为用。对此,朱熹的得意门生陈淳亦有颇为恰当的阐释:
文公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以两句对言之,何也?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见于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天理其体而人事其用也。“仪”谓容仪而形见于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与“文”字相应。“则”谓法则、准则,是个骨子,所以存于中者,乃确然不易之意,与“节”字相应。文而后仪,节而后则,必有天理之节文而后有人事之仪则。言须尽此二者,意乃圆备。④
陈淳认为,“天理之节文”与“人事之仪则”是相对而言的,“天理”在中,对应“人事”在外,“节”“则”在中,对应“文”“仪”在外,“天理其体”对应“人事其用”,而“节文”为“事宜”;天理为“体”,相应的,作为“事宜”之“节文”自然为用。这是深得朱熹本意的。
朱熹视“天理”为体、“节文”为用,以体之“天理”和用之“节文”并释“礼”,意在突出“礼”兼备体用,这正是朱熹“礼”之释的高明之处。《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有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
人只是合当做底便是体,人做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如尺与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铢,则体也;将去秤量物事,则用也。①
朱熹持“礼”之体用兼备观,明确批驳“公江西有般乡谈”,意在反对“江西”陆学之认虚空者为体,好比尺无寸、秤无星,自然无尺秤之用。朱熹认为,按照天理、规矩去做,就是礼之体,这里强调的是做的“合当”性,不强调做本身,因为做本身(“做处”)就是用,如此一来,作为“合当做”的礼就同时具备体和用,就如体用兼备的扇子,柄、骨子、纸糊等是体,“人摇之”是用,两者绝不能截然分开。与此类似的论述还出现在朱熹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如其《答赵致道》言:
不曰理而曰礼者,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故圣人之言体用兼该、本末一贯。②
总而言之,朱熹释“礼”为“天理之节文”,兼备体用,一方面体现出其形而上的“天理”之“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兼顾其形而下的“节文”之“用”的特征,对“礼”的体用做了充分展示,凸显了他倡导的“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①的学术旨趣。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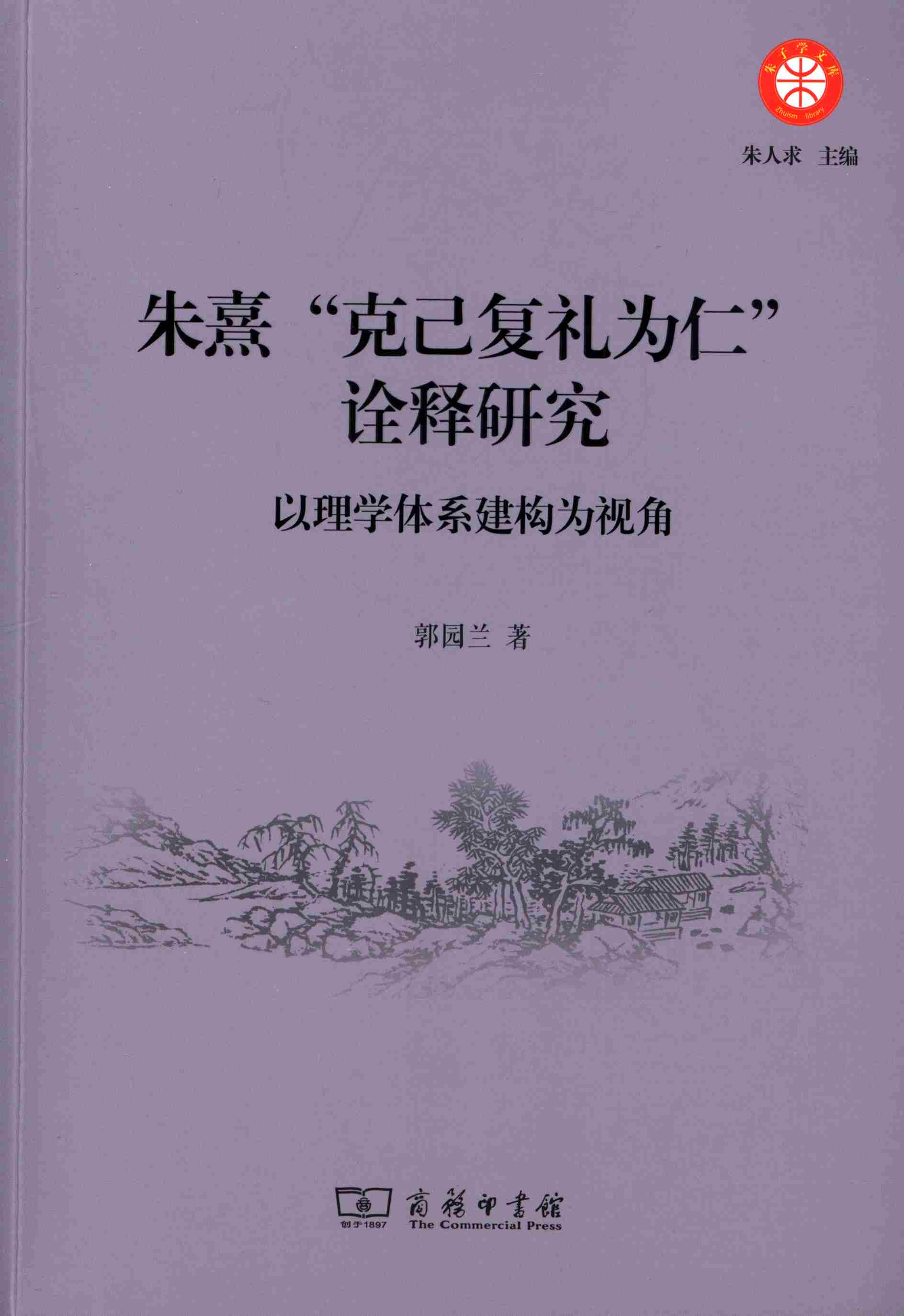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以宋代佛道挑战、清代汉宋之争为背景,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挖掘朱熹克己、复礼、为仁及三者关系的诠释意涵,揭示其诠释的理学化、阶段性、发展性、矛盾性特征及其成因,彰显了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与深远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