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背景与意义
| 内容出处: |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599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背景与意义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3 |
| 页码: | 1-13 |
| 摘要: | 本文内容主要探讨了“克己复礼为仁”这一重要命题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朱熹对这一命题的重视。这一命题是孔子的核心理论之一,包含了“仁”和“礼”两个关键词,在《论语》等先秦典籍中频繁出现。朱熹在其学术中特别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并从多个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诠释和研究,包括“克己”、“礼”和“仁”等关键术语。 |
| 关键词: | 朱熹 克己复礼 哲学思想 |
内容
一、“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学的重要命题
“克己复礼为仁”始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理解“克己复礼为仁”是掌握孔子思想的关键。孔门之教,要旨在“克己复礼”,①“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仁礼学说的核心”②。“克己复礼为仁”之重要体现为这一命题中包含了两个关键词“仁”和“礼”。此章节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仁”这个概念特征的。③
从现象来看,“仁”和“礼”在《论语》中出现频率高,被讨论次数多。《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其中作为孔子的道德标准105次,仁人3次,同“人”1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④,“礼”出现了74次(包括指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等;《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八佾》“林放问礼之本”一事)①。先秦其他典籍中“仁”“礼”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在《左传》中,“仁”出现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62次,礼121次。②
从思想本质来看,“仁”和“礼”在孔子学说中地位重要,是孔子理论的主脉,是儒家思想系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劳思光指出,“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故就其基本理论言之,‘仁、义、礼’三观念,为孔子理论之主脉,至于其他理论,则皆可视为此一基本理论之引申发挥”;“‘礼’观念是孔子学说之始点”,“‘仁’观念是孔子学说之中心”。③赵光贤认为,“‘仁’与‘礼’两个概念在孔子学说中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④。杨国荣指出,“孔子在对‘仁’做创造性阐发的同时,也将‘礼’提到突出地位,从而,其学说也表现为‘仁’和‘礼’两者的统一”,“儒学以‘仁’和‘礼’的统一为其核心”。⑤颜炳罡强调,“仁与礼是儒家思想系统中两个基本范畴”,“‘克己复礼为仁’体现着主观与客观、常道与变道、绝对与相对的合一,即仁与礼的合一”。⑥梁涛亦认为,“从孔子开始,儒家之道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仁,一是礼”,“仁是孔子开创之新统……礼是孔子承继之旧统”。⑦
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的“仁”和“礼”思想,了解儒家学术的传承、创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经典诠释的特征、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品格。
二、“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朱熹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
朱熹重视“克己复礼”,早在43岁撰写《克斋记》时强调:“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①朱熹特别指出求仁之术很多,而“克己复礼”足以概括其要领。朱熹欣赏颜子,朱熹“心中所想像之颜子,乃与东汉以下迄于北宋理学诸儒所想像者有绝大之不同。朱子想像中之颜子,乃是刚健果决,具有一种极强之内力,能勇猛精进,如天旋地转,雷动风行做将去。如将百万兵,操纵在我,拱揖指挥如意”②。朱熹将颜子魅力归于“克己复礼”,“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③。颜子“克己复礼”工夫直做了上一截,仲弓“主敬”只做得下一截。与当时理学家看重仲弓不同,朱熹更进一层,透到人心内在力量,从“克己”角度欣赏颜子:“夫子告颜渊之言,非大段刚明者,不足以当之”;“孔子答颜子处,是就心上说工夫,较深密为难”;“颜子克己,如红炉上一点雪”;“克己复礼,若火烈烈,则莫我敢遏”。④
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多有措意,具体体现为他对这一命题中“克己”“礼”“仁”三个关键术语的重视。朱熹重视“克己”,到晚年甚至专崇“克己”,置“克己”于“主敬”工夫之上。对此,钱穆曾指出,朱子“克己”思想乃两宋理学思想中甚值注意研讨之问题,并扼腕叹息言程朱之学者不曾触及朱子“克己”之研究。⑤朱熹对“礼”颇为关注,撰写《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释“礼”为“天理之节文”,既重视“礼”之形而上的理学理论建构⑥,又重视礼之形而下的践履。朱熹重视“仁”,早年即与其师李侗讨论“仁”字之说①,中年又与张栻等湖湘学者进行仁说之辩,并撰写《仁说》②,晚年一如既往地关注仁之论题③。朱熹重视“仁”,尤为重视“克己复礼为仁”之“仁”:“《论语》只说仁”;“《论语》切要处在言仁。言仁处多,某未识门路。日用至亲切处,觉在告颜子一章”。④钱穆指出,朱熹“以仁字释理气,乃见其亲切人生,而天人两界之诚为一体,盖至是而义据通深,可以无憾”⑤。陈来强调,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理学、仁学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甚至从凸显朱熹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的角度,把朱熹仁学摆在高于理学的位置。⑥
可见,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有助于深入理解朱熹学术。
三、“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内含朱熹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之使命
仁礼关系是儒学的核心问题,孔子对仁礼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对于前者,朱熹的诠释较为简略,而对于后者,朱熹予以详细诠释,并将其纳入理学体系中进行了深度诠释。佛道挑战、儒学式微、人心陷溺、价值颠覆等问题迫切需要朱熹彰显仁与礼的价值,“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承载着朱熹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建构理学的学术使命。
唐宋以来,佛道日炽。佛道特别是佛教,注重心性建构,拥有完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对儒学构成极大挑战,早在中唐韩愈、李翱就对佛教的盛行颇为忧虑,其中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⑦,坚定而激烈地反佛拒佛。到了宋代,被全祖望称为开宋代学术之先河的孙复更是大声疾呼,视佛老之徒横行中国为儒者耻辱。宋代儒者纷纷叹息佛门昌盛,忧虑道学失传,意识到佛教患达千年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学不振,进而以复兴儒学为自身使命。
与前人不同的是,朱熹集两宋学术之大成,又曾出入佛老,其应对佛老挑战,一方面学习佛老之长,弥补儒学之短。能“入室操戈”,吸收和“整合”佛道思想①,汲取佛家精致的本体思想和思辨的心性理论,主动加强本体形上世界、心性论和工夫论建构,加强儒学统摄人心的作用,生发仁体观念,建立自己的心性哲学,守护儒家的价值。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以“天理”释礼,沟通礼、理,凸显仁体,强调“若更要真识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谓‘克己复礼’;克去己私,如何便唤得做仁”②,“克去己私”的结果就是呈现“仁之体”。正因如此,陈来先生强调,“是佛道二氏使得儒家的仁体论被逼显出来”③。
另一方面,驳斥佛老之短,彰显儒学之长。一是与佛老开展“虚实之辨”,凸显儒学与佛老之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强调儒家以“仁义礼智”为性,突出儒家所言之“理”为“实理”,批评佛家“作用释性”,批驳佛老“溺于空虚”。朱熹以“理”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反复强调的即是儒家这一实理不同于佛老的空虚。二是光大儒家礼义,以礼义这一儒家之本作为战胜佛教的法宝。欧阳修指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④;孙复亦认为,“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⑤,兴王道、正人伦都离不开这一根本。朱熹在诠释克己、复礼二者关系时,特别突出儒家“复礼”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力避佛老之空寂,在为弟子廖子晦作的《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中,更是严厉批评佛老“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虚空无实。①
朱熹以“胜身之私欲”释“克己”,一方面,以理学体系特有的概念,在理学体系大框架下进行诠释,使诠释理学化,以贯彻其天理人欲观,体现其理学本体论思想;另一方面,“己”“礼”相对,以“天理”对治“人欲”,以此解决朱熹所处南宋时期亟需解决的人心陷溺、价值沦丧的现实危机。正因如此,朱熹“克己”诠释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在朱熹等新儒家学者的头脑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内心的思想,他们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倾向于转向内在。②
四、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
汉学、宋学在“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上存在分野,清代汉学家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对朱熹等宋学家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了全面批驳,对此,清代学者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站在朱熹等宋代理学家的立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驳。③
清代汉学家以“修身”训“克己”,反驳朱熹等宋学家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毛奇龄、惠士奇等从训诂上批评朱熹释“己”为“己私”是添字解经,阮元、陈澧、戴东原等又指出,以“己私”释“己”,与“为仁由己”之“己”的释义不同,导致同一文本上下文文义不一致。毛奇龄、焦循、陈澧还从源头入手,溯源纠谬,稽查宋儒“克己”解谬误之出处与流变。④方东树反驳,称汉学家著书,睥睨程朱,一派妄说,粗谬已极。
清代汉学家以“礼”代“理”,反驳宋儒以“理”释“礼”。戴震、焦循禁言理,认为宋儒言性言理,“以理为学”,“探之茫茫,索之冥冥”,“如风如影”;方东树认为宋儒所谓理,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存所发自然之条理”,是实理、实德,不曾茫茫冥冥,“实事求是,莫如程朱”。江藩认为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对此,方东树则认为,宋儒性命之旨就是礼乐之源,自汉晋以来,唯独宋儒周程诸子,能知其本源合一处。
清代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仁”①,咎责朱熹以“心德”释“仁”为谬误。阮元在其《揅经室集》之《论语论仁论》中发挥郑玄“相人偶”注解,并结合曾子“人相与”和孟子“仁者人也”等释义,认为一个人独居闭户,谈不到仁,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认定仁字是指两人相人偶的关系。②方东树反驳认为,以“人偶”论“仁”之用则可,以之论“仁”之体,则不可,程子以“爱非仁”“仁性爱情”言仁之体,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发明程子意最详尽。
关于汉宋之别,阮元和刘师培从源头上加以区分。阮元说:“汉唐注疏之学,乃荀子之流衍,宋明心性之学,乃孟子之流衍,汉宋之别,亦犹荀孟之别也。”③阮视汉唐注疏之学与宋明心性之学为荀、孟的流布,把汉宋之别区分为荀、孟之分。后来,刘师培进一步强调:“曾子、子思、孟子皆成一家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者也,是为汉学之祖。”④刘以曾子、子思、孟子自成一家之言,为宋学之祖,以子夏、荀子为传六艺之学者,为汉学之祖。不过,就发端而言,孔子均具师儒之长,汉学、宋学都渊源于孔子,都是得孔学之一端发展而成,都是孔学道统的继承人。梁涛认为,“孔子思想中的不同倾向,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分化,不仅表现为仁学与礼学的对立,还衍化为汉学与宋学的分歧”—。与阮、刘不同的是,梁指出汉宋之分是孟、荀分化的衍化,仁礼对立是孟、荀分化的表现。
在阮、刘、梁等人看来,汉学家主宗荀子,宋学家主宗孟子,孟荀有别,仁礼相对,汉宋论争。不过,汉学家宋学家固然有宗孟宗荀、偏仁偏礼之区别,但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中的同一仁、礼以及克己,汉宋学者的诠释亦迥然不同,可见,汉宋学者诠释不同,与宗孟宗荀、偏仁偏礼并无必然联系,朱熹在理学建构视角下,结合天理人欲、专言偏言、理一分殊、体用等理学专门术语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而清代汉学家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其实,清代汉学家与朱熹等宋学家的最大隔阂并不在于宗孟还是宗荀、崇仁还是尚礼,而在于他们学术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不同的问题意识致使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共情,尤其是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理学体系建构采取的是漠然和抵斥的态度,他们驳斥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自然有失公允。由此可见,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非常重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不无裨益。
五、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彰显了儒学的分化和发展
南宋之前比较完整的《论语》注本主要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宋初邢①《论语注疏》等三者。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而邢昺《论语注疏》则敷衍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而成。这三本注解《论语》之作,对“克己复礼”章均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其诠释主要说明外在客观的礼仪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形塑,并未太在意内在道德修养对个体的影响。朱熹《论语集注》刊出后,邢昺《论语注疏》式微②,《论语集注》成为注解《论语》的新权威。《论语》为语录体著作,注者多为随文疏解,阐释文本时很难做到完整和系统。朱子将原本独立的《论语》与《大学》《孟子》《中庸》结合,使《论语》从《五经》系统转而归属《四书》系统,并用集结《四书》的义理脉络诠释《论语》。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是一个转捩点,与之前的诠释存在重大差异,体现出宋代思想家对儒学价值核心的不同见解。
朱子不仅在《论语集注》“颜渊”篇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而且在《论语集注》的其他篇章中,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朱子语类》①“颜渊”篇及其他篇章中不断深化对“克己复礼”的诠释。朱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富于创造性,主动承担起社会道德调节使命,引导道德由外在的制约规范转变为个体的内在要求。跟原初儒学“仁”“礼”并重不同的是,朱熹视“仁”“礼”相通并重的同时,又有将“仁”学引向心性之学,抬高“仁”,推动“仁”“礼”分离的趋向。②如果说原初儒学为“周孔之道”,那么整体来看,宋代儒学崇“孔孟之道”。考察和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不难发现,儒学在宋代有了分化和发展。
趋向分化的宋代儒学在明代又进一步分化和发展,这由王阳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可见一斑。时异代易,面临新的社会情境,阳明与朱子学术思想体系亦有歧异。王阳明释“己”为“私欲”、“理”为天理,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朱子大略相同,但他批评朱子“克己复礼”之“效验”说就“用”不就“体”,主张克己复礼与立志、意诚相结合,就“体”而言,“克己复礼”是复吾心一体之仁。王阳明“克己复礼”诠释以良知之学为主,以德性为本,以良知代替“仁”,“仁”的地位更进一步提高,“礼”的诠释更趋于内在化、本体化,心即礼,从而以礼为心性,以仁消融礼,更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分化。
直至明末,“由于儒者痛感水间林下空谈心性之无补于世道,才觉悟到儒学之体绝不限于‘良知之独体’,而必须回向经典、重求内向外王之整体”①,阳明后学如罗汝芳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之教,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特别强调“礼”的意义,逐步走向考察礼文、遵守礼法之路,“礼”的地位逐渐抬升,儒学分化有回缩之势。其诠释方法一反阳明之纯义理,表现为义理、训诂兼用,意识到以道问学成就尊德性,博文约礼。钱穆提出“每转益进说”②,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③,二者都是针对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而提出的,也可用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我们可通过内在理路的视角来阐释学术发展脉络。据此,明代思想家“克己复礼”诠释究竟系“宋明思想脉络”,承前接宋代,更多表现出与朱子诠释的一致性呢,还是系“明清思想脉络”,启后续清代,更多表现出与朱子诠释的相异性,从而使清代思想成为明代思想之继起性展开呢?中国台湾学者林月惠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克己复礼”,支持前说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眼于社会背景来研究“克己复礼”,证实后者⑤。
时至清代,清初学者王夫之亲历明朝灭亡之哀,痛感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着重批判了儒者只重视“克己”而轻视“复礼”的倾向,主张“复礼”努力的必要性。①清代中期学者与之不同,多将目光投向朱子,对朱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诠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们较少直接、正面地进行义理诠释,而以训诂考据的方法解经,通过批判朱子等诠释来表现其“克己复礼为仁”思想。凌廷堪《复礼上》,以“礼”为首出,主张以“礼”摄“仁”、融“仁”于“礼”,认为“仁”抽象而无形,“礼”则具体而有形,“仁”必依于“礼”而后可见。凌廷堪持“礼”本论、“礼”先于“仁”之说。杨国荣指出,“从实质的层面看,儒学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仁’和‘礼’的分离以及两者的单向展开。在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各自阐发,便已展现以上分化。孟子侧重‘仁’;荀子更注重‘礼’,肯定‘学至乎礼而止矣。’孟荀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原初儒学所包含的‘仁’和‘礼’”②。如果说宋代儒学有单向抬高“仁”的趋向,明代儒学进一步分化发展到“仁”消融礼,那么阳明后学、晚明罗汝芳则有重视礼的趋向,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是主张“复礼”,而到了清代中期,凌廷堪等视礼为首出,走向重礼、“以礼代理”甚至“礼消融仁”之路了。
可见,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有助于了解儒学在宋代的分化和发展,亦可以此类推,把握明、清儒学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
六、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能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③分周公、孔子两大步,第一步是“由巫到礼”,第二步是“释礼归仁”,①提倡“儒学四期说”②,以周(由巫到礼,政治脱魅)、孔(建构情理,释礼归仁)替代“儒学三期说”(牟宗三)的孔、孟,认为道德形上学挽救不了也复兴不了中国,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要期待于“礼”的完善,即良好的国家体制。颜炳罡提出“依仁以成礼”和“设礼以显仁”两种儒学发展方式。③杨国荣力图在更高历史层面回到“仁”和“礼”统一的原初儒学。④梁涛则提出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构建儒家新道统的期盼。⑤当代学人从“仁”“礼”视域,关怀着儒学发展,为儒学的未来把脉。从理学体系建构的独特视角深入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形成、内涵和发展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面临外来佛教、本土道教冲击时是如何积极应对的,儒学面临不同社会政治问题时是如何创造性地进行理论建设的,这恰恰能够为我们认识儒学、发展儒学提供借鉴和思考,能引导我们与时俱进,直面当今社会问题,全面促进儒学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学的重要命题,“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朱熹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为了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朱熹建构理学,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朱熹的经典诠释与理学建构相互作用。而朱熹建构理学,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理学化的诠释又遭到了清代汉学家的漠视与针锋相对的驳斥,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可见,不论是朱熹应对佛老挑战、复兴儒学,还是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的漠视和驳斥,都聚焦于朱熹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理学建构,这意味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非常必要和重要。
以理学体系建构这一视角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不仅可以透过朱熹经典诠释和理学建构的互动,深入理解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内涵和朱熹的学术特征,还有助于了解宋代乃至明代、清代儒学的分化和发展,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不无裨益,亦可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从而彰显出朱熹的经典诠释在儒学发展史上深远的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
“克己复礼为仁”始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理解“克己复礼为仁”是掌握孔子思想的关键。孔门之教,要旨在“克己复礼”,①“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仁礼学说的核心”②。“克己复礼为仁”之重要体现为这一命题中包含了两个关键词“仁”和“礼”。此章节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仁”这个概念特征的。③
从现象来看,“仁”和“礼”在《论语》中出现频率高,被讨论次数多。《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其中作为孔子的道德标准105次,仁人3次,同“人”1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④,“礼”出现了74次(包括指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等;《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八佾》“林放问礼之本”一事)①。先秦其他典籍中“仁”“礼”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在《左传》中,“仁”出现39次,“礼”为517次。在《国语》中,仁62次,礼121次。②
从思想本质来看,“仁”和“礼”在孔子学说中地位重要,是孔子理论的主脉,是儒家思想系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劳思光指出,“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故就其基本理论言之,‘仁、义、礼’三观念,为孔子理论之主脉,至于其他理论,则皆可视为此一基本理论之引申发挥”;“‘礼’观念是孔子学说之始点”,“‘仁’观念是孔子学说之中心”。③赵光贤认为,“‘仁’与‘礼’两个概念在孔子学说中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④。杨国荣指出,“孔子在对‘仁’做创造性阐发的同时,也将‘礼’提到突出地位,从而,其学说也表现为‘仁’和‘礼’两者的统一”,“儒学以‘仁’和‘礼’的统一为其核心”。⑤颜炳罡强调,“仁与礼是儒家思想系统中两个基本范畴”,“‘克己复礼为仁’体现着主观与客观、常道与变道、绝对与相对的合一,即仁与礼的合一”。⑥梁涛亦认为,“从孔子开始,儒家之道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仁,一是礼”,“仁是孔子开创之新统……礼是孔子承继之旧统”。⑦
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的“仁”和“礼”思想,了解儒家学术的传承、创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经典诠释的特征、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品格。
二、“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朱熹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
朱熹重视“克己复礼”,早在43岁撰写《克斋记》时强调:“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①朱熹特别指出求仁之术很多,而“克己复礼”足以概括其要领。朱熹欣赏颜子,朱熹“心中所想像之颜子,乃与东汉以下迄于北宋理学诸儒所想像者有绝大之不同。朱子想像中之颜子,乃是刚健果决,具有一种极强之内力,能勇猛精进,如天旋地转,雷动风行做将去。如将百万兵,操纵在我,拱揖指挥如意”②。朱熹将颜子魅力归于“克己复礼”,“颜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复礼’四个字”③。颜子“克己复礼”工夫直做了上一截,仲弓“主敬”只做得下一截。与当时理学家看重仲弓不同,朱熹更进一层,透到人心内在力量,从“克己”角度欣赏颜子:“夫子告颜渊之言,非大段刚明者,不足以当之”;“孔子答颜子处,是就心上说工夫,较深密为难”;“颜子克己,如红炉上一点雪”;“克己复礼,若火烈烈,则莫我敢遏”。④
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多有措意,具体体现为他对这一命题中“克己”“礼”“仁”三个关键术语的重视。朱熹重视“克己”,到晚年甚至专崇“克己”,置“克己”于“主敬”工夫之上。对此,钱穆曾指出,朱子“克己”思想乃两宋理学思想中甚值注意研讨之问题,并扼腕叹息言程朱之学者不曾触及朱子“克己”之研究。⑤朱熹对“礼”颇为关注,撰写《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释“礼”为“天理之节文”,既重视“礼”之形而上的理学理论建构⑥,又重视礼之形而下的践履。朱熹重视“仁”,早年即与其师李侗讨论“仁”字之说①,中年又与张栻等湖湘学者进行仁说之辩,并撰写《仁说》②,晚年一如既往地关注仁之论题③。朱熹重视“仁”,尤为重视“克己复礼为仁”之“仁”:“《论语》只说仁”;“《论语》切要处在言仁。言仁处多,某未识门路。日用至亲切处,觉在告颜子一章”。④钱穆指出,朱熹“以仁字释理气,乃见其亲切人生,而天人两界之诚为一体,盖至是而义据通深,可以无憾”⑤。陈来强调,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理学、仁学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甚至从凸显朱熹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的角度,把朱熹仁学摆在高于理学的位置。⑥
可见,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有助于深入理解朱熹学术。
三、“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内含朱熹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之使命
仁礼关系是儒学的核心问题,孔子对仁礼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对于前者,朱熹的诠释较为简略,而对于后者,朱熹予以详细诠释,并将其纳入理学体系中进行了深度诠释。佛道挑战、儒学式微、人心陷溺、价值颠覆等问题迫切需要朱熹彰显仁与礼的价值,“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中承载着朱熹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建构理学的学术使命。
唐宋以来,佛道日炽。佛道特别是佛教,注重心性建构,拥有完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对儒学构成极大挑战,早在中唐韩愈、李翱就对佛教的盛行颇为忧虑,其中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⑦,坚定而激烈地反佛拒佛。到了宋代,被全祖望称为开宋代学术之先河的孙复更是大声疾呼,视佛老之徒横行中国为儒者耻辱。宋代儒者纷纷叹息佛门昌盛,忧虑道学失传,意识到佛教患达千年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学不振,进而以复兴儒学为自身使命。
与前人不同的是,朱熹集两宋学术之大成,又曾出入佛老,其应对佛老挑战,一方面学习佛老之长,弥补儒学之短。能“入室操戈”,吸收和“整合”佛道思想①,汲取佛家精致的本体思想和思辨的心性理论,主动加强本体形上世界、心性论和工夫论建构,加强儒学统摄人心的作用,生发仁体观念,建立自己的心性哲学,守护儒家的价值。朱熹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以“天理”释礼,沟通礼、理,凸显仁体,强调“若更要真识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谓‘克己复礼’;克去己私,如何便唤得做仁”②,“克去己私”的结果就是呈现“仁之体”。正因如此,陈来先生强调,“是佛道二氏使得儒家的仁体论被逼显出来”③。
另一方面,驳斥佛老之短,彰显儒学之长。一是与佛老开展“虚实之辨”,凸显儒学与佛老之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强调儒家以“仁义礼智”为性,突出儒家所言之“理”为“实理”,批评佛家“作用释性”,批驳佛老“溺于空虚”。朱熹以“理”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礼”,反复强调的即是儒家这一实理不同于佛老的空虚。二是光大儒家礼义,以礼义这一儒家之本作为战胜佛教的法宝。欧阳修指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④;孙复亦认为,“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⑤,兴王道、正人伦都离不开这一根本。朱熹在诠释克己、复礼二者关系时,特别突出儒家“复礼”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力避佛老之空寂,在为弟子廖子晦作的《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中,更是严厉批评佛老“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虚空无实。①
朱熹以“胜身之私欲”释“克己”,一方面,以理学体系特有的概念,在理学体系大框架下进行诠释,使诠释理学化,以贯彻其天理人欲观,体现其理学本体论思想;另一方面,“己”“礼”相对,以“天理”对治“人欲”,以此解决朱熹所处南宋时期亟需解决的人心陷溺、价值沦丧的现实危机。正因如此,朱熹“克己”诠释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在朱熹等新儒家学者的头脑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内心的思想,他们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倾向于转向内在。②
四、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
汉学、宋学在“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上存在分野,清代汉学家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对朱熹等宋学家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了全面批驳,对此,清代学者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站在朱熹等宋代理学家的立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驳。③
清代汉学家以“修身”训“克己”,反驳朱熹等宋学家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毛奇龄、惠士奇等从训诂上批评朱熹释“己”为“己私”是添字解经,阮元、陈澧、戴东原等又指出,以“己私”释“己”,与“为仁由己”之“己”的释义不同,导致同一文本上下文文义不一致。毛奇龄、焦循、陈澧还从源头入手,溯源纠谬,稽查宋儒“克己”解谬误之出处与流变。④方东树反驳,称汉学家著书,睥睨程朱,一派妄说,粗谬已极。
清代汉学家以“礼”代“理”,反驳宋儒以“理”释“礼”。戴震、焦循禁言理,认为宋儒言性言理,“以理为学”,“探之茫茫,索之冥冥”,“如风如影”;方东树认为宋儒所谓理,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存所发自然之条理”,是实理、实德,不曾茫茫冥冥,“实事求是,莫如程朱”。江藩认为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对此,方东树则认为,宋儒性命之旨就是礼乐之源,自汉晋以来,唯独宋儒周程诸子,能知其本源合一处。
清代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仁”①,咎责朱熹以“心德”释“仁”为谬误。阮元在其《揅经室集》之《论语论仁论》中发挥郑玄“相人偶”注解,并结合曾子“人相与”和孟子“仁者人也”等释义,认为一个人独居闭户,谈不到仁,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认定仁字是指两人相人偶的关系。②方东树反驳认为,以“人偶”论“仁”之用则可,以之论“仁”之体,则不可,程子以“爱非仁”“仁性爱情”言仁之体,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发明程子意最详尽。
关于汉宋之别,阮元和刘师培从源头上加以区分。阮元说:“汉唐注疏之学,乃荀子之流衍,宋明心性之学,乃孟子之流衍,汉宋之别,亦犹荀孟之别也。”③阮视汉唐注疏之学与宋明心性之学为荀、孟的流布,把汉宋之别区分为荀、孟之分。后来,刘师培进一步强调:“曾子、子思、孟子皆成一家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者也,是为汉学之祖。”④刘以曾子、子思、孟子自成一家之言,为宋学之祖,以子夏、荀子为传六艺之学者,为汉学之祖。不过,就发端而言,孔子均具师儒之长,汉学、宋学都渊源于孔子,都是得孔学之一端发展而成,都是孔学道统的继承人。梁涛认为,“孔子思想中的不同倾向,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分化,不仅表现为仁学与礼学的对立,还衍化为汉学与宋学的分歧”—。与阮、刘不同的是,梁指出汉宋之分是孟、荀分化的衍化,仁礼对立是孟、荀分化的表现。
在阮、刘、梁等人看来,汉学家主宗荀子,宋学家主宗孟子,孟荀有别,仁礼相对,汉宋论争。不过,汉学家宋学家固然有宗孟宗荀、偏仁偏礼之区别,但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中的同一仁、礼以及克己,汉宋学者的诠释亦迥然不同,可见,汉宋学者诠释不同,与宗孟宗荀、偏仁偏礼并无必然联系,朱熹在理学建构视角下,结合天理人欲、专言偏言、理一分殊、体用等理学专门术语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而清代汉学家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其实,清代汉学家与朱熹等宋学家的最大隔阂并不在于宗孟还是宗荀、崇仁还是尚礼,而在于他们学术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不同的问题意识致使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共情,尤其是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理学体系建构采取的是漠然和抵斥的态度,他们驳斥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自然有失公允。由此可见,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非常重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不无裨益。
五、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彰显了儒学的分化和发展
南宋之前比较完整的《论语》注本主要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宋初邢①《论语注疏》等三者。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而邢昺《论语注疏》则敷衍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而成。这三本注解《论语》之作,对“克己复礼”章均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其诠释主要说明外在客观的礼仪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形塑,并未太在意内在道德修养对个体的影响。朱熹《论语集注》刊出后,邢昺《论语注疏》式微②,《论语集注》成为注解《论语》的新权威。《论语》为语录体著作,注者多为随文疏解,阐释文本时很难做到完整和系统。朱子将原本独立的《论语》与《大学》《孟子》《中庸》结合,使《论语》从《五经》系统转而归属《四书》系统,并用集结《四书》的义理脉络诠释《论语》。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是一个转捩点,与之前的诠释存在重大差异,体现出宋代思想家对儒学价值核心的不同见解。
朱子不仅在《论语集注》“颜渊”篇诠释“克己复礼为仁”,而且在《论语集注》的其他篇章中,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朱子语类》①“颜渊”篇及其他篇章中不断深化对“克己复礼”的诠释。朱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富于创造性,主动承担起社会道德调节使命,引导道德由外在的制约规范转变为个体的内在要求。跟原初儒学“仁”“礼”并重不同的是,朱熹视“仁”“礼”相通并重的同时,又有将“仁”学引向心性之学,抬高“仁”,推动“仁”“礼”分离的趋向。②如果说原初儒学为“周孔之道”,那么整体来看,宋代儒学崇“孔孟之道”。考察和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不难发现,儒学在宋代有了分化和发展。
趋向分化的宋代儒学在明代又进一步分化和发展,这由王阳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可见一斑。时异代易,面临新的社会情境,阳明与朱子学术思想体系亦有歧异。王阳明释“己”为“私欲”、“理”为天理,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朱子大略相同,但他批评朱子“克己复礼”之“效验”说就“用”不就“体”,主张克己复礼与立志、意诚相结合,就“体”而言,“克己复礼”是复吾心一体之仁。王阳明“克己复礼”诠释以良知之学为主,以德性为本,以良知代替“仁”,“仁”的地位更进一步提高,“礼”的诠释更趋于内在化、本体化,心即礼,从而以礼为心性,以仁消融礼,更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分化。
直至明末,“由于儒者痛感水间林下空谈心性之无补于世道,才觉悟到儒学之体绝不限于‘良知之独体’,而必须回向经典、重求内向外王之整体”①,阳明后学如罗汝芳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之教,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特别强调“礼”的意义,逐步走向考察礼文、遵守礼法之路,“礼”的地位逐渐抬升,儒学分化有回缩之势。其诠释方法一反阳明之纯义理,表现为义理、训诂兼用,意识到以道问学成就尊德性,博文约礼。钱穆提出“每转益进说”②,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③,二者都是针对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而提出的,也可用于“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我们可通过内在理路的视角来阐释学术发展脉络。据此,明代思想家“克己复礼”诠释究竟系“宋明思想脉络”,承前接宋代,更多表现出与朱子诠释的一致性呢,还是系“明清思想脉络”,启后续清代,更多表现出与朱子诠释的相异性,从而使清代思想成为明代思想之继起性展开呢?中国台湾学者林月惠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克己复礼”,支持前说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着眼于社会背景来研究“克己复礼”,证实后者⑤。
时至清代,清初学者王夫之亲历明朝灭亡之哀,痛感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其“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着重批判了儒者只重视“克己”而轻视“复礼”的倾向,主张“复礼”努力的必要性。①清代中期学者与之不同,多将目光投向朱子,对朱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诠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们较少直接、正面地进行义理诠释,而以训诂考据的方法解经,通过批判朱子等诠释来表现其“克己复礼为仁”思想。凌廷堪《复礼上》,以“礼”为首出,主张以“礼”摄“仁”、融“仁”于“礼”,认为“仁”抽象而无形,“礼”则具体而有形,“仁”必依于“礼”而后可见。凌廷堪持“礼”本论、“礼”先于“仁”之说。杨国荣指出,“从实质的层面看,儒学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仁’和‘礼’的分离以及两者的单向展开。在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各自阐发,便已展现以上分化。孟子侧重‘仁’;荀子更注重‘礼’,肯定‘学至乎礼而止矣。’孟荀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原初儒学所包含的‘仁’和‘礼’”②。如果说宋代儒学有单向抬高“仁”的趋向,明代儒学进一步分化发展到“仁”消融礼,那么阳明后学、晚明罗汝芳则有重视礼的趋向,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是主张“复礼”,而到了清代中期,凌廷堪等视礼为首出,走向重礼、“以礼代理”甚至“礼消融仁”之路了。
可见,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有助于了解儒学在宋代的分化和发展,亦可以此类推,把握明、清儒学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
六、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能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③分周公、孔子两大步,第一步是“由巫到礼”,第二步是“释礼归仁”,①提倡“儒学四期说”②,以周(由巫到礼,政治脱魅)、孔(建构情理,释礼归仁)替代“儒学三期说”(牟宗三)的孔、孟,认为道德形上学挽救不了也复兴不了中国,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要期待于“礼”的完善,即良好的国家体制。颜炳罡提出“依仁以成礼”和“设礼以显仁”两种儒学发展方式。③杨国荣力图在更高历史层面回到“仁”和“礼”统一的原初儒学。④梁涛则提出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构建儒家新道统的期盼。⑤当代学人从“仁”“礼”视域,关怀着儒学发展,为儒学的未来把脉。从理学体系建构的独特视角深入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形成、内涵和发展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面临外来佛教、本土道教冲击时是如何积极应对的,儒学面临不同社会政治问题时是如何创造性地进行理论建设的,这恰恰能够为我们认识儒学、发展儒学提供借鉴和思考,能引导我们与时俱进,直面当今社会问题,全面促进儒学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学的重要命题,“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朱熹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为了应对佛道挑战、复兴儒学,朱熹建构理学,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了理学化的诠释,朱熹的经典诠释与理学建构相互作用。而朱熹建构理学,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理学化的诠释又遭到了清代汉学家的漠视与针锋相对的驳斥,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可见,不论是朱熹应对佛老挑战、复兴儒学,还是清代汉学家对朱熹的漠视和驳斥,都聚焦于朱熹的“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与理学建构,这意味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非常必要和重要。
以理学体系建构这一视角研究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不仅可以透过朱熹经典诠释和理学建构的互动,深入理解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内涵和朱熹的学术特征,还有助于了解宋代乃至明代、清代儒学的分化和发展,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不无裨益,亦可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从而彰显出朱熹的经典诠释在儒学发展史上深远的影响和鲜活的生命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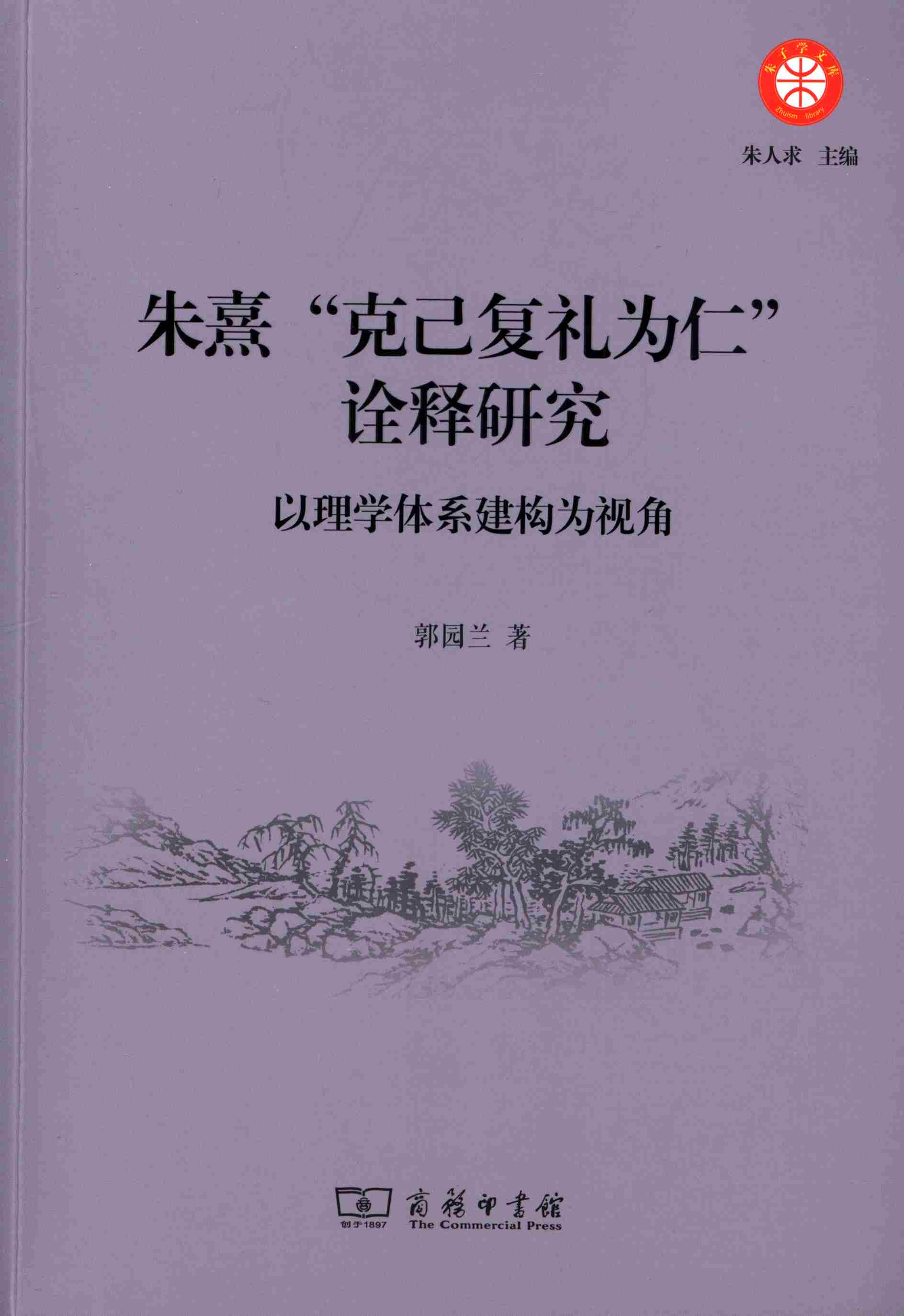
《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研究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以宋代佛道挑战、清代汉宋之争为背景,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对朱熹“克己复礼为仁”诠释进行研究,挖掘朱熹克己、复礼、为仁及三者关系的诠释意涵,揭示其诠释的理学化、阶段性、发展性、矛盾性特征及其成因,彰显了朱熹内倾的学术特征、“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与深远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