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 内容出处: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96 |
| 颗粒名称: | 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36-145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朱子理学中的“理一分殊”观念与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念的相似性、相异性和特别之处。文章指出,这两种观念都试图解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问题,但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朱子理学强调理的统一性和分的多样性,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理的统一;而佛教华严宗则强调理事的无碍融合,通过悟境的实现来达到理的统一。这两种观念在处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见解和方法,对于理解东亚文化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
| 关键词: | 朱子理学 儒家文化 朱熹 |
内容
“理一分殊”是理学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而此命题与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理学的“理一分殊”与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究竟有何相似、相异及特别之处,是本文试图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方二元论的弊端
无论是朱子理学的“理一分殊”或是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探讨的都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之间的关系。对此,西方哲人其实也一直很感兴趣。然而,西方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却与东方完全不同。比如古希腊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也就是说,现象世界就是形而下、无常的俗世,而理念世界就是形而上、永恒超脱的雅世。然而,在西方哲人的眼中,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是对立为二的。不论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斯多德也好,都是在整个宇宙的结构中划了一道中分线,中分线以上的形而上(界),在中分线以下的形而下(界)。而这一道鸿沟产生了之后,他们就很难把这个形而上同形而下的世界给联系起来。
肯定一个神圣的世界,并向往与追求,这本身是人类进步的好现象。然而,倘若将上下层世界对立起来就会产生很多严重的弊端。试想,假若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抛弃了下层世界而变做雅人、雅士,都变成艺术家或至高的道德人格以及真理的追求者。那么,对于下层世界的黑暗、罪恶、痛苦、烦恼又将要交给谁呢?如此,只会导致下层的世界越来越堕落,而上层世界越来越飘渺了。虽然在后来,这种对哲学的追求转变成了以拯救世俗为目标的宗教。然而,由于二元对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宗教对待世俗的态度必然是傲慢的。宗教根本瞧不起世俗,而世俗世界却有太多巨细、复杂、困难的问题需要人们认真耐心地一一应对。对于这些,宗教都不屑于面对,那么宗教必然没有真正应对现实世界的能力。因此这样的宗教只是导致更多的人逃避现实而已。
除此之外,此二元对立论还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即产生极端恐怖主义思想。这些恐怖分子渴望极端自由的思想,然而在现实世界里面,并没有他的存身之地,于是他想毁掉别人,甚至把一切的他人全都毁掉,最后只剩下他自己而形成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因为唯有如此,他的精神才能够得到自由。
那么,是否可以在二元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呢?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们想尽了各种方法,可是结果不是偏向唯实论就是偏向唯心论,没有人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致到了当代,人们纷纷又陷入了以物质看齐而忽视信仰的另一个极端。
然而,在古老的东方,思想家们早已就二元融合的问题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论证。这些论证就体现在佛教的“理事圆融”与理学的“理一分殊”之中。
二、佛教华严的“理事圆融”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由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过程。
佛教的小乘思想就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想。小乘佛学思想强调现世一切皆苦,现世是罪恶、黑暗、痛苦、无知的领域。因此,小乘佛学便认为最高的理想世界不在此生此世,而要另求一个他生他世。小乘佛学只知道痛恨这个世界、诅咒这个世界,表现在他的生活领域上没有自力、没有自由、不能自在,处处感到受到拘束、胁迫、不自由、不自在。因此,他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他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他理想的实现。而这样的世界观,与中国人的文化理想是相当不一致的。因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由介绍小乘转而发展大乘。
根据华严宗的判教方法,在大乘里还发展形成大乘空宗(大乘始教)、大乘有宗(大乘终教)、大乘顿教以及大乘圆教。具体而言,大乘反对空无所有的断灭空,强调以“空空”来纠正顽空的错误,意思是我们谈空的时候,要把那个空也要空掉,这样才不会堕落于断灭空中。可是双离必定两失,讲到最后还是没有寄托,没有一物足以信赖。
于是,佛教中又出现了要透过大乘始教的说法而畅谈“事理圆融”的大乘终教。大乘终教提出,若要讲空,则为不碍有的空,若要讲有,则是不碍空的有。由于有不自有,空不自空,空有二见必须要达到自在圆融而不相碍,然后便能融化成亦空亦有,非空非有。至此在大乘终教中提出了二元融合的问题,这种二元融合的问题在佛教中被称为中道的哲学。
怎样将亦空亦有、非空非有的二元融合的中道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呢?佛教各宗派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如在法相唯识宗里,说明世界缘起问题的,为了避免小乘佛学里面的业惑缘起,而提出另一个出发点,即缘起于善恶纠缠在一起的“如来藏藏识”。然而此时的佛教又进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讲“空宗”时,空宗会有堕入顽空的危险;讲“有宗”时,又不得不承认有宗里面又会夹杂许多不纯洁的成分。
紧接着在中国又出现了“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的大乘顿教。大乘顿教强调“言语道断,心处行灭”,所以顿悟则必须走到“语观双绝门”的路途上来。然而,标榜不立文字的禅宗,有一部分人沦落成了随心所欲的狂禅,还有一部分人也堕入种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文字障里面去了。因此从华严宗的立场看来,大乘顿教还未透彻,没有真正讲到圆融,依然未能达到圆教自在无碍的境地。
那么,华严宗是怎样论证圆教自在无碍的境地呢?当所有的人都在探讨业惑缘起或是染净交织的阿赖耶识缘起的时候,华严初祖杜顺大师提出了法界缘起。此法界为一真法界,是真实不虚、如常不变的真如,即佛教的法身,也就是二元论里形而上却真实存在、永恒不变的理。因此这个法界缘起的哲学思想上面,并不是割裂的、分析的一套观念,而是综合的、统贯的一套观念。换句话说,它并不是凭借一个有限的概念、有限的范畴来说明整个的世界,而是把哲学上面最初的起点,容纳到“无穷”思想体系里面,看出无穷性的美满,然后从那个地方找出一个可以解释世界,解释人生的起点——那就是佛性、法性的起点。这个理与事不是分割为二的,而是由理而诞生了事,因此事事都包含着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杜顺大师还提出了“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法界三观这样的概念。所谓“真空观”,首先肯定真实不虚、如常不变的一真法界在其哲学体系中起点和统贯地位。但是,永恒之理与无常之事又该如何消除对立性呢?面对这一问题,杜顺大师除了真空观以外,还引用了第二观“理事无碍观”来对治。杜顺认为,由于事源于理,虽然理事不同,但是理事绝不是对立的二件事,理与事之间的矛盾性是可以去除掉的。因此,杜顺引用了梵文里面的一个名词,即“无碍”。因为理和事虽然事两种重要的范畴,但它们可以折衷,可以和谐而不冲突。也就是说虽然是两个“相反”,但是也是“相成”的;因为是“相成”,所以说可以两相调和而无碍,这个关系互相沟通之后就变成了“理事无碍观”。至于第三观就是“周遍含容观”,因为我们已经把二元对立因素的矛盾性给点化掉后,变成为不再是“相反”而是“相成”。进而在“相成”的里面,便产生了广大的和谐作用,事和事的和谐,理和理的和谐;而且在这广大的和谐里面,彼此间丝毫没有任何事和理的差别与矛盾感及对立感。因此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当你站在理的立场可以忘掉事,站在事的立场可以忘掉理,因为理同事、事同理都已经圆融和谐到像水乳交融的状态。在水乳交融的状态里面,我们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的矛盾感,所以对于理并不执着于理,对于事也不执着于事。这样子以来,一方面我们可以穷究到最高的精神领域,但是我们不必停留,马上又可以返回到现实世界的底层,而且是能来去自如。同时对于内外、主客之间的隔阂均能化消。因此,在杜顺大师的“周遍含容观”里面,我们可以通彻上下,贯通内外、左右、主客,我们的精神领域可以随时随地对流无碍,而不再停滞于某一种境界里面。
后来的华严祖师们,便由杜顺大师的法界三观,再把世界的秘密展开来,变成四种基本形式的法界:第一种叫“理法界”;第二种是“事法界”;第三种是是就“关系”的立场,使理事沟通起来而成为和谐,叫做“理事无碍法界”;第四种是“事事无碍法界”。其中最麻烦的就是处理现实世界上面的各种事情,因为在这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差别事项,在它们中间很难把它们贯通起来。但是在华严宗的思想领域内,它能把这种无碍的观念发展到普遍的哲学原理之中。如此,我们可以说在理性世界上面能够适合应用,在现实世界领域也能使用,在理事融贯的境界里面还可以用。因此华严宗的哲学一发展到第四代的澄观大师时,便特别重视事事无碍法界。他将前面的缘起论、法界三观、四法界这三方面的哲学理论再扩充成为一套根本的本体论,叫做“十玄门”,又叫“十玄缘起”,引用很深微奥妙的道理来说明何以理性会具有无限的应用,任何事情都可以根据理性而加以彻底的说明。这样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总相、别相、同相、成相、坏相的“六相圆融”的思想,然后在那里便形成广大的和谐性。可以说,当我们把华严宗变成哲学智慧来说,它是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用来说明宇宙人生是怎么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观点来做不同的说明。而且在不同的说明层次里面,我们要来说明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到底这四法界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中间的关系如果能给予彻底的了解之后,那么最后将能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典型。①
三、理学中的“理一分殊”
理学则是通过“理一分殊”的理论将传统原本只是指导人们应该如何处世的儒学上升到富含思辨论证的哲学范畴,从而使儒学从由外向内死板的约束转向了由内向外理所应当的自觉。可以说,正是由于“理一分殊”这一缜密的理论体系,使儒学成为了融思辨与实用的理学。而理学也因此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宋至清代600余年间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
理学中“理一分殊”这一名词的出现源于程颐对其弟子杨时的答疑解惑。杨时在读张载所作之《西铭》时,提出了“疑其近于兼爱”的疑问。原来作为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的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是秦汉以来儒家学者的“大弊”②。而孟子则认为人人都可通过充分扩充自己生而即具的心之“善端”,来挺立自己德性人格,与天相契一体,达至“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人要想成其为人,就必须与天相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具有了超越性,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为使儒家学者“心于天道”,①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形上根据,张载撰写了体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生命流行的宇宙图景之《西铭》。然而敏锐的杨时却发现在民胞物与的一片和谐之中,似乎同墨家的兼爱说一样都犯了“言体而不及用”的错误。在杨时看来,墨家兼爱虽然也属“仁者事”,说出了应该遍爱他人、他物的道理,但因“不及用”缺失了“仁之方”。也就是说,杨时怀疑张载强调民胞物与的同时是否忽视了不同的人与事之间的差别,望其师能够指点一套可在现实人生中可以实施儒学之义的为学工夫,以推明《西铭》提出的“民胞物与”理想对现实人生的指导作用。
针对杨时的质疑,程颐答复如下:
《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注: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注: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②
在这里,程颐首揭“理一而分殊”这一术语。程颐指出,墨子无分别的兼爱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本体,一是形而上纯善的本体,二是形而下、善恶交杂、错综复杂的事也被毫无区别地视为本体。因此墨子只能善恶不分、无差别地兼爱了。然而张载的民胞物与则与墨子不同。因为张载只承认形而上这一纯善的本体,形而下的只能称为事而非本体。然而纯善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事却并非毫无关联。因为形而下的事事虽然各自不同,然而形而上的理却毫无保留地贯注在一切不同的事之中。正是因为理就如同血液一样贯注在所有民众与所有事物之中,所以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为此程颐还进一步解释到,如果只强调事事的分殊,那么人们对待不同的人和事的态度就会很冷漠甚至很残酷;可是如果事事又不加以区分,又会像墨子一样善恶不分、无差别地兼爱了。张载认为道学的理一分殊,一方面强调分殊之中要想尽办法推进到理一的境界,由此就能激发人们内心仁爱从而避免唯我独尊、自私自利,而这也是仁爱得以推行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又强调虽然事事之中都贯注着一理,但是事事毕竟是不同的,不能无差别地对待,从而避免如同墨子一样因兼爱到无义的程度。因此程颐对杨时说,你将道学中的民胞物与与墨子的兼爱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墨子的兼爱只看到了本体却没有看到用处的不同。墨子希望通过兼爱推行到每个人的身上,但是却错误地将本体无差别地用在了用处,这样反而起不到推行真正纯善本体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道学与墨学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只承认一个形而上的本体,并且认为形而上的本体是贯注在每一个形而下的人与事上这样的理事关系,是华严宗与理学所共同深深认可的。正是在共同理事关系的指导下,华严宗与理学都共同强调要将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相反相成地联系起来。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二者在理事关系上观点是如此一致,为何理学家们依然将佛教视为劲敌,且个个都展示出不把佛教消灭誓不罢休的姿态呢?
四、华严“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之区别在如何理解一理和万理的关系中,程颐承认了华严宗与理学的相似性。据《遗书》所载:
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①
当有人提到佛教华严宗的义理,并让程颐给予评价时,程颐答道“万理归于一理”,可见程颐也是理解华严的理事观的。然而,当人们继续问程颐“未知所以破它处”时,程颐却这样答道:
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诸子个个谈仁谈义,只为他归宿处不是,只是个自私。为轮回生死,却为释氏之辞善遁,才穷着他,便道我不为这个,到了写在册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浅近处,只烧一文香,便道我有无穷福利,怀却这个心,怎生事神明?释氏言成住坏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坏,无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尽便枯坏也。他以谓如木之生,生长既足却自住,然后却渐渐毁坏。天下之物,无有住者。婴儿一生,长一日便是减一日,何尝得住?然而气体日渐长大,长的自长,减的自减,自不相干也。”
问释氏理障之说。曰:“释氏有此说,谓既明此理,而又执持是理,故为障。此错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个理,既明此理,夫复何障?若以理为障,则是己与理为二。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①
程颐说,虽然佛教也谈仁谈义,但是它导致的结果与儒学不同。程颐认为,佛教以生死轮回的论断吸引人们信佛,这样,人们信佛的初衷就不对,其导致的结果最终依旧只能是自私。程颐说,释氏之辞善遁,说如果这样问佛僧,佛僧会回答,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此。然而程颐认为,佛书上清清楚楚地写到生死轮回,佛教是无法回避的。程颐又说,佛教中还有烧一柱香就能得无穷福利的说法,这样明显是投机取巧,根本无法真正提升人们的素质,更不用说达到本体一样神明的境界。程颐还指出,佛教中提到“成、住、坏、空”,程颐认为,事实上只有成、坏,没有住、空。又有人问到,佛教有一种视理为障的说法,不知程颐如何看待。程颐认为,释氏虽然知道理,却又执着于这个理,所以才将这个理视为障。其实是释氏看错了这个理。程颐说,天下只有一个理,又怎么会成为障碍呢?如果将理视为障碍,那就是将自己与理分为二,而不是合一了。最后,程颐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释氏虽然在平日里高谈性命之学,但是事实上对于世事却毫无了解。因此,程颐认为,佛教理论只能高谈阔论,实际上却不能从中获得有益于人们实际生活的东西。
这样看来,程颐对佛教的批判似乎分析得很合理。然而,实际上,佛教却并不是程颐所说的这样简单。上文已经提到,中国佛教由小乘发展到大乘直到华严,是经过不断地深入反思与努力调适而形成的。不能因为小乘的错误而否认大乘及华严的理论。除此之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极其复杂的。大乘佛教强调普度众生,就是要给一切根机的人都予以说法的机会,因此大乘佛教用了很多权宜的方法,目的是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机会亲近佛教。而且在亲近佛教之后,佛教还要用各式各样非常复杂的方法,想尽办法让不同根机的人最终都能够迁善改过,达到共同提升的目的。还必须一提的是,佛教中本就鱼龙混杂,若将含混在佛教中不成熟的人和事来概括佛教,这样对待佛教似乎未免也有失公允。
然而,由于佛教强调“圆融”,华严宗在一理通于万事的理论指导下,一再强调理与事、事与事之间完全可以互相贯通从而上升到理一的境界。因此佛教更相信所有一切都可以通过圆融的方式统一起来,即错的也可以变为对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所以即使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世界观完全相反,可是大乘佛教却并没有完全否认小乘,而是努力通过十分圆融的方式,让小乘也转为大乘。
而理学家们则认为“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因而更重视“分殊”理论的建设与论证。比如“理气论”,朱熹在吸收前人思想精华之后,就借助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气”,用以说明理派生万物,而万物却不同的发展过程。朱熹认为,理如果离开气就无安顿处,天理必须安顿在人的形气之中。然而“气”是形而下的范畴,它不仅使原本统一的理分别成了不同的事,更使纯善的天理因形而下气之污染而构成不同层次的事。因此,理学家们紧紧抓住了气所造成的不同层次,一再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朱熹指出:
《西铭》本不是说孝,只是说事天,但推事亲之心以事天耳。……盖事亲却未免有正有不正处。若天道纯然,则无正不正之处,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①
由此可见,朱子认为可以通过事天之理来证明事亲之理。因为天道纯然,无正不正之处,所以事亲及事君之理也同样不需要过多加以考虑,因为这就是天理。这正是因为如此,纲常伦理成为了理所应当之事,理学家们认为,这是维护社会秩序必然的途径。
五、小结
在探讨理学“理一分殊”与佛教华严“理事无碍”关系的过程中,有人认为,理学家们是受到华严的理事关系才启发出了“理一分殊”;而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论的人们则相信,华严理论也是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笔者认为,其实对于这一逻辑思想的来源没有必要过多纠结其来源。因为印度本有“梵我如一”之说法,而中国《易经》中也早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样的理论源头。可以说华严、理学的理事观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然而,华严宗的事事无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所解决是每个人的终极信仰问题,在承认事事之差别的基础上,通过理一的认识,从而达到共同提升之理想。而理学则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通过理一而分殊证实差别的客观性,从而要求人们各安其职、各守其份,最终达成社会和谐的愿望。可以说,华严依然更重视理一,而理学则更重视分殊。然而遗憾的是,本可以殊途同归的二者却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如何将理一与分殊真正地圆融无碍地统一起来,是古人留给今人的宝贵理论,也是一个今人还必须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原刊于《中国佛学》2017年第1期)
一、西方二元论的弊端
无论是朱子理学的“理一分殊”或是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探讨的都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之间的关系。对此,西方哲人其实也一直很感兴趣。然而,西方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却与东方完全不同。比如古希腊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也就是说,现象世界就是形而下、无常的俗世,而理念世界就是形而上、永恒超脱的雅世。然而,在西方哲人的眼中,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是对立为二的。不论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斯多德也好,都是在整个宇宙的结构中划了一道中分线,中分线以上的形而上(界),在中分线以下的形而下(界)。而这一道鸿沟产生了之后,他们就很难把这个形而上同形而下的世界给联系起来。
肯定一个神圣的世界,并向往与追求,这本身是人类进步的好现象。然而,倘若将上下层世界对立起来就会产生很多严重的弊端。试想,假若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抛弃了下层世界而变做雅人、雅士,都变成艺术家或至高的道德人格以及真理的追求者。那么,对于下层世界的黑暗、罪恶、痛苦、烦恼又将要交给谁呢?如此,只会导致下层的世界越来越堕落,而上层世界越来越飘渺了。虽然在后来,这种对哲学的追求转变成了以拯救世俗为目标的宗教。然而,由于二元对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宗教对待世俗的态度必然是傲慢的。宗教根本瞧不起世俗,而世俗世界却有太多巨细、复杂、困难的问题需要人们认真耐心地一一应对。对于这些,宗教都不屑于面对,那么宗教必然没有真正应对现实世界的能力。因此这样的宗教只是导致更多的人逃避现实而已。
除此之外,此二元对立论还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即产生极端恐怖主义思想。这些恐怖分子渴望极端自由的思想,然而在现实世界里面,并没有他的存身之地,于是他想毁掉别人,甚至把一切的他人全都毁掉,最后只剩下他自己而形成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因为唯有如此,他的精神才能够得到自由。
那么,是否可以在二元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呢?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们想尽了各种方法,可是结果不是偏向唯实论就是偏向唯心论,没有人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致到了当代,人们纷纷又陷入了以物质看齐而忽视信仰的另一个极端。
然而,在古老的东方,思想家们早已就二元融合的问题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论证。这些论证就体现在佛教的“理事圆融”与理学的“理一分殊”之中。
二、佛教华严的“理事圆融”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由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过程。
佛教的小乘思想就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想。小乘佛学思想强调现世一切皆苦,现世是罪恶、黑暗、痛苦、无知的领域。因此,小乘佛学便认为最高的理想世界不在此生此世,而要另求一个他生他世。小乘佛学只知道痛恨这个世界、诅咒这个世界,表现在他的生活领域上没有自力、没有自由、不能自在,处处感到受到拘束、胁迫、不自由、不自在。因此,他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他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他理想的实现。而这样的世界观,与中国人的文化理想是相当不一致的。因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由介绍小乘转而发展大乘。
根据华严宗的判教方法,在大乘里还发展形成大乘空宗(大乘始教)、大乘有宗(大乘终教)、大乘顿教以及大乘圆教。具体而言,大乘反对空无所有的断灭空,强调以“空空”来纠正顽空的错误,意思是我们谈空的时候,要把那个空也要空掉,这样才不会堕落于断灭空中。可是双离必定两失,讲到最后还是没有寄托,没有一物足以信赖。
于是,佛教中又出现了要透过大乘始教的说法而畅谈“事理圆融”的大乘终教。大乘终教提出,若要讲空,则为不碍有的空,若要讲有,则是不碍空的有。由于有不自有,空不自空,空有二见必须要达到自在圆融而不相碍,然后便能融化成亦空亦有,非空非有。至此在大乘终教中提出了二元融合的问题,这种二元融合的问题在佛教中被称为中道的哲学。
怎样将亦空亦有、非空非有的二元融合的中道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呢?佛教各宗派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如在法相唯识宗里,说明世界缘起问题的,为了避免小乘佛学里面的业惑缘起,而提出另一个出发点,即缘起于善恶纠缠在一起的“如来藏藏识”。然而此时的佛教又进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讲“空宗”时,空宗会有堕入顽空的危险;讲“有宗”时,又不得不承认有宗里面又会夹杂许多不纯洁的成分。
紧接着在中国又出现了“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的大乘顿教。大乘顿教强调“言语道断,心处行灭”,所以顿悟则必须走到“语观双绝门”的路途上来。然而,标榜不立文字的禅宗,有一部分人沦落成了随心所欲的狂禅,还有一部分人也堕入种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文字障里面去了。因此从华严宗的立场看来,大乘顿教还未透彻,没有真正讲到圆融,依然未能达到圆教自在无碍的境地。
那么,华严宗是怎样论证圆教自在无碍的境地呢?当所有的人都在探讨业惑缘起或是染净交织的阿赖耶识缘起的时候,华严初祖杜顺大师提出了法界缘起。此法界为一真法界,是真实不虚、如常不变的真如,即佛教的法身,也就是二元论里形而上却真实存在、永恒不变的理。因此这个法界缘起的哲学思想上面,并不是割裂的、分析的一套观念,而是综合的、统贯的一套观念。换句话说,它并不是凭借一个有限的概念、有限的范畴来说明整个的世界,而是把哲学上面最初的起点,容纳到“无穷”思想体系里面,看出无穷性的美满,然后从那个地方找出一个可以解释世界,解释人生的起点——那就是佛性、法性的起点。这个理与事不是分割为二的,而是由理而诞生了事,因此事事都包含着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杜顺大师还提出了“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法界三观这样的概念。所谓“真空观”,首先肯定真实不虚、如常不变的一真法界在其哲学体系中起点和统贯地位。但是,永恒之理与无常之事又该如何消除对立性呢?面对这一问题,杜顺大师除了真空观以外,还引用了第二观“理事无碍观”来对治。杜顺认为,由于事源于理,虽然理事不同,但是理事绝不是对立的二件事,理与事之间的矛盾性是可以去除掉的。因此,杜顺引用了梵文里面的一个名词,即“无碍”。因为理和事虽然事两种重要的范畴,但它们可以折衷,可以和谐而不冲突。也就是说虽然是两个“相反”,但是也是“相成”的;因为是“相成”,所以说可以两相调和而无碍,这个关系互相沟通之后就变成了“理事无碍观”。至于第三观就是“周遍含容观”,因为我们已经把二元对立因素的矛盾性给点化掉后,变成为不再是“相反”而是“相成”。进而在“相成”的里面,便产生了广大的和谐作用,事和事的和谐,理和理的和谐;而且在这广大的和谐里面,彼此间丝毫没有任何事和理的差别与矛盾感及对立感。因此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当你站在理的立场可以忘掉事,站在事的立场可以忘掉理,因为理同事、事同理都已经圆融和谐到像水乳交融的状态。在水乳交融的状态里面,我们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的矛盾感,所以对于理并不执着于理,对于事也不执着于事。这样子以来,一方面我们可以穷究到最高的精神领域,但是我们不必停留,马上又可以返回到现实世界的底层,而且是能来去自如。同时对于内外、主客之间的隔阂均能化消。因此,在杜顺大师的“周遍含容观”里面,我们可以通彻上下,贯通内外、左右、主客,我们的精神领域可以随时随地对流无碍,而不再停滞于某一种境界里面。
后来的华严祖师们,便由杜顺大师的法界三观,再把世界的秘密展开来,变成四种基本形式的法界:第一种叫“理法界”;第二种是“事法界”;第三种是是就“关系”的立场,使理事沟通起来而成为和谐,叫做“理事无碍法界”;第四种是“事事无碍法界”。其中最麻烦的就是处理现实世界上面的各种事情,因为在这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差别事项,在它们中间很难把它们贯通起来。但是在华严宗的思想领域内,它能把这种无碍的观念发展到普遍的哲学原理之中。如此,我们可以说在理性世界上面能够适合应用,在现实世界领域也能使用,在理事融贯的境界里面还可以用。因此华严宗的哲学一发展到第四代的澄观大师时,便特别重视事事无碍法界。他将前面的缘起论、法界三观、四法界这三方面的哲学理论再扩充成为一套根本的本体论,叫做“十玄门”,又叫“十玄缘起”,引用很深微奥妙的道理来说明何以理性会具有无限的应用,任何事情都可以根据理性而加以彻底的说明。这样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总相、别相、同相、成相、坏相的“六相圆融”的思想,然后在那里便形成广大的和谐性。可以说,当我们把华严宗变成哲学智慧来说,它是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用来说明宇宙人生是怎么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观点来做不同的说明。而且在不同的说明层次里面,我们要来说明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到底这四法界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中间的关系如果能给予彻底的了解之后,那么最后将能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典型。①
三、理学中的“理一分殊”
理学则是通过“理一分殊”的理论将传统原本只是指导人们应该如何处世的儒学上升到富含思辨论证的哲学范畴,从而使儒学从由外向内死板的约束转向了由内向外理所应当的自觉。可以说,正是由于“理一分殊”这一缜密的理论体系,使儒学成为了融思辨与实用的理学。而理学也因此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宋至清代600余年间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
理学中“理一分殊”这一名词的出现源于程颐对其弟子杨时的答疑解惑。杨时在读张载所作之《西铭》时,提出了“疑其近于兼爱”的疑问。原来作为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的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是秦汉以来儒家学者的“大弊”②。而孟子则认为人人都可通过充分扩充自己生而即具的心之“善端”,来挺立自己德性人格,与天相契一体,达至“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人要想成其为人,就必须与天相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具有了超越性,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为使儒家学者“心于天道”,①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形上根据,张载撰写了体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生命流行的宇宙图景之《西铭》。然而敏锐的杨时却发现在民胞物与的一片和谐之中,似乎同墨家的兼爱说一样都犯了“言体而不及用”的错误。在杨时看来,墨家兼爱虽然也属“仁者事”,说出了应该遍爱他人、他物的道理,但因“不及用”缺失了“仁之方”。也就是说,杨时怀疑张载强调民胞物与的同时是否忽视了不同的人与事之间的差别,望其师能够指点一套可在现实人生中可以实施儒学之义的为学工夫,以推明《西铭》提出的“民胞物与”理想对现实人生的指导作用。
针对杨时的质疑,程颐答复如下:
《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注: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注: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②
在这里,程颐首揭“理一而分殊”这一术语。程颐指出,墨子无分别的兼爱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本体,一是形而上纯善的本体,二是形而下、善恶交杂、错综复杂的事也被毫无区别地视为本体。因此墨子只能善恶不分、无差别地兼爱了。然而张载的民胞物与则与墨子不同。因为张载只承认形而上这一纯善的本体,形而下的只能称为事而非本体。然而纯善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事却并非毫无关联。因为形而下的事事虽然各自不同,然而形而上的理却毫无保留地贯注在一切不同的事之中。正是因为理就如同血液一样贯注在所有民众与所有事物之中,所以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为此程颐还进一步解释到,如果只强调事事的分殊,那么人们对待不同的人和事的态度就会很冷漠甚至很残酷;可是如果事事又不加以区分,又会像墨子一样善恶不分、无差别地兼爱了。张载认为道学的理一分殊,一方面强调分殊之中要想尽办法推进到理一的境界,由此就能激发人们内心仁爱从而避免唯我独尊、自私自利,而这也是仁爱得以推行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又强调虽然事事之中都贯注着一理,但是事事毕竟是不同的,不能无差别地对待,从而避免如同墨子一样因兼爱到无义的程度。因此程颐对杨时说,你将道学中的民胞物与与墨子的兼爱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墨子的兼爱只看到了本体却没有看到用处的不同。墨子希望通过兼爱推行到每个人的身上,但是却错误地将本体无差别地用在了用处,这样反而起不到推行真正纯善本体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道学与墨学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只承认一个形而上的本体,并且认为形而上的本体是贯注在每一个形而下的人与事上这样的理事关系,是华严宗与理学所共同深深认可的。正是在共同理事关系的指导下,华严宗与理学都共同强调要将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相反相成地联系起来。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二者在理事关系上观点是如此一致,为何理学家们依然将佛教视为劲敌,且个个都展示出不把佛教消灭誓不罢休的姿态呢?
四、华严“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之区别在如何理解一理和万理的关系中,程颐承认了华严宗与理学的相似性。据《遗书》所载:
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①
当有人提到佛教华严宗的义理,并让程颐给予评价时,程颐答道“万理归于一理”,可见程颐也是理解华严的理事观的。然而,当人们继续问程颐“未知所以破它处”时,程颐却这样答道:
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诸子个个谈仁谈义,只为他归宿处不是,只是个自私。为轮回生死,却为释氏之辞善遁,才穷着他,便道我不为这个,到了写在册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浅近处,只烧一文香,便道我有无穷福利,怀却这个心,怎生事神明?释氏言成住坏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坏,无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尽便枯坏也。他以谓如木之生,生长既足却自住,然后却渐渐毁坏。天下之物,无有住者。婴儿一生,长一日便是减一日,何尝得住?然而气体日渐长大,长的自长,减的自减,自不相干也。”
问释氏理障之说。曰:“释氏有此说,谓既明此理,而又执持是理,故为障。此错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个理,既明此理,夫复何障?若以理为障,则是己与理为二。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①
程颐说,虽然佛教也谈仁谈义,但是它导致的结果与儒学不同。程颐认为,佛教以生死轮回的论断吸引人们信佛,这样,人们信佛的初衷就不对,其导致的结果最终依旧只能是自私。程颐说,释氏之辞善遁,说如果这样问佛僧,佛僧会回答,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此。然而程颐认为,佛书上清清楚楚地写到生死轮回,佛教是无法回避的。程颐又说,佛教中还有烧一柱香就能得无穷福利的说法,这样明显是投机取巧,根本无法真正提升人们的素质,更不用说达到本体一样神明的境界。程颐还指出,佛教中提到“成、住、坏、空”,程颐认为,事实上只有成、坏,没有住、空。又有人问到,佛教有一种视理为障的说法,不知程颐如何看待。程颐认为,释氏虽然知道理,却又执着于这个理,所以才将这个理视为障。其实是释氏看错了这个理。程颐说,天下只有一个理,又怎么会成为障碍呢?如果将理视为障碍,那就是将自己与理分为二,而不是合一了。最后,程颐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释氏虽然在平日里高谈性命之学,但是事实上对于世事却毫无了解。因此,程颐认为,佛教理论只能高谈阔论,实际上却不能从中获得有益于人们实际生活的东西。
这样看来,程颐对佛教的批判似乎分析得很合理。然而,实际上,佛教却并不是程颐所说的这样简单。上文已经提到,中国佛教由小乘发展到大乘直到华严,是经过不断地深入反思与努力调适而形成的。不能因为小乘的错误而否认大乘及华严的理论。除此之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极其复杂的。大乘佛教强调普度众生,就是要给一切根机的人都予以说法的机会,因此大乘佛教用了很多权宜的方法,目的是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机会亲近佛教。而且在亲近佛教之后,佛教还要用各式各样非常复杂的方法,想尽办法让不同根机的人最终都能够迁善改过,达到共同提升的目的。还必须一提的是,佛教中本就鱼龙混杂,若将含混在佛教中不成熟的人和事来概括佛教,这样对待佛教似乎未免也有失公允。
然而,由于佛教强调“圆融”,华严宗在一理通于万事的理论指导下,一再强调理与事、事与事之间完全可以互相贯通从而上升到理一的境界。因此佛教更相信所有一切都可以通过圆融的方式统一起来,即错的也可以变为对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所以即使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世界观完全相反,可是大乘佛教却并没有完全否认小乘,而是努力通过十分圆融的方式,让小乘也转为大乘。
而理学家们则认为“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因而更重视“分殊”理论的建设与论证。比如“理气论”,朱熹在吸收前人思想精华之后,就借助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气”,用以说明理派生万物,而万物却不同的发展过程。朱熹认为,理如果离开气就无安顿处,天理必须安顿在人的形气之中。然而“气”是形而下的范畴,它不仅使原本统一的理分别成了不同的事,更使纯善的天理因形而下气之污染而构成不同层次的事。因此,理学家们紧紧抓住了气所造成的不同层次,一再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朱熹指出:
《西铭》本不是说孝,只是说事天,但推事亲之心以事天耳。……盖事亲却未免有正有不正处。若天道纯然,则无正不正之处,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①
由此可见,朱子认为可以通过事天之理来证明事亲之理。因为天道纯然,无正不正之处,所以事亲及事君之理也同样不需要过多加以考虑,因为这就是天理。这正是因为如此,纲常伦理成为了理所应当之事,理学家们认为,这是维护社会秩序必然的途径。
五、小结
在探讨理学“理一分殊”与佛教华严“理事无碍”关系的过程中,有人认为,理学家们是受到华严的理事关系才启发出了“理一分殊”;而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论的人们则相信,华严理论也是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笔者认为,其实对于这一逻辑思想的来源没有必要过多纠结其来源。因为印度本有“梵我如一”之说法,而中国《易经》中也早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样的理论源头。可以说华严、理学的理事观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然而,华严宗的事事无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所解决是每个人的终极信仰问题,在承认事事之差别的基础上,通过理一的认识,从而达到共同提升之理想。而理学则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通过理一而分殊证实差别的客观性,从而要求人们各安其职、各守其份,最终达成社会和谐的愿望。可以说,华严依然更重视理一,而理学则更重视分殊。然而遗憾的是,本可以殊途同归的二者却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如何将理一与分殊真正地圆融无碍地统一起来,是古人留给今人的宝贵理论,也是一个今人还必须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原刊于《中国佛学》2017年第1期)
附注
①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6~277页。
②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页。
①张载自述创作《西铭》的心迹为:“只欲学者心于天道,若语道则不须如是言。”(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13页)
②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9页。
①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9页。
①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9页。
①《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22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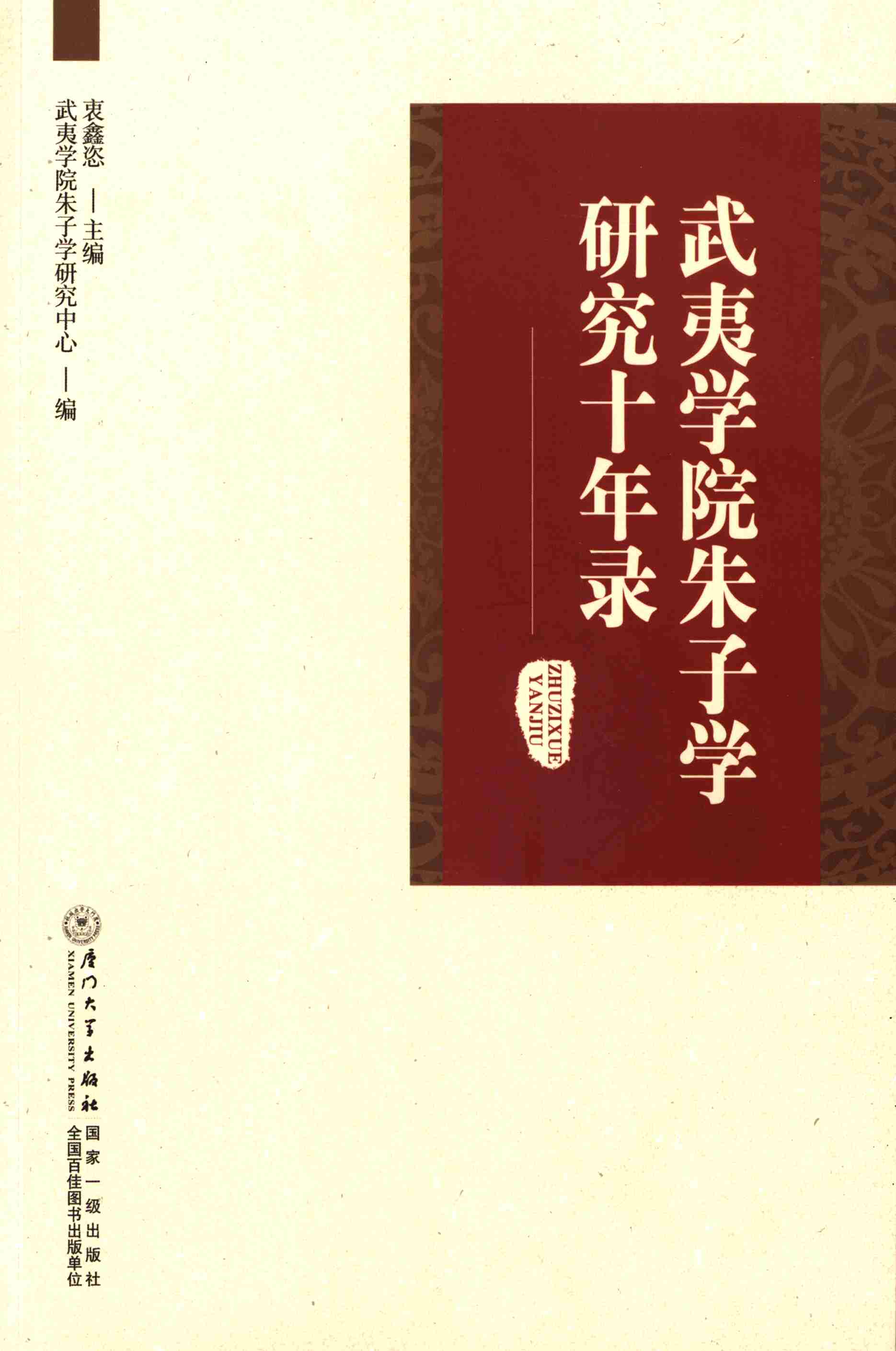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