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儒结党,明儒结社
| 内容出处: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95 |
| 颗粒名称: | 二、宋儒结党,明儒结社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6 |
| 页码: | 130-135 |
| 摘要: |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宋明两代的三次“党锢”,揭示了士大夫集团在政治斗争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程朱道学与阳明道学在团体化上的差异表现在,程朱道学主动参与权力制衡或斗争,并通过服饰的统一强化团体认同;而阳明道学则更注重教育民众,传播学术思想。这种差异的形成与两宋的政治氛围和明朝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
| 关键词: | 阳明道学 儒家文化 朱熹 |
内容
现在来说说程朱道学与阳明道学在团体化上的差异。有两个词,政党化、社团化,二者同中有异。政党化意味着主动参与权力制衡或斗争,社团化则无。套到余英时先生所阐发的宋儒“致君行道”、明儒“觉民行道”的两条路线之分,可以说,宋儒是自觉结党的(政党化),明儒只做到自觉结社(社团化)。鉴于明朝敌视士人的政治氛围,王阳明一门的弘道独辟蹊径,绕着政治走,虽然同样大力讲学授徒,自成团体,其表达却是很内敛的。学界的相关研究已多,①这里补充一点关于服饰的,以见程朱党性的张扬,与阳明学派的不敢示人以党性。
宋代反道学者攻击道学时,往往提到道学者独特的着装——宽衣、博带、缁冠、幅巾、黑履等等——也就是朱熹《家礼》力图复活的周礼“深衣”制度。南宋初年言者称伊川之徒“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可见朱熹之前的道学群体已因服饰之故而被当成另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司马温公依《礼记》做深衣、冠簪、幅巾、缙带。”②这些为朱熹所直接继承。但他继承程颐多少,则有疑问。古代服饰中确有名“程子巾”(实为冠)者,但程颐是否推广过格外醒目的幅巾,尚无更多史料可资佐证。至于朱熹,则毫无疑问为道学人士设计了十分独特的服饰。《道命录》卷七下“言者论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载一位言官的反感之语:
臣闻此徒盛炽之时,宽衣博带,高谈阔论,或沉默不言,则其口似瘖,或蹁跹不趋,则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时,儒者事也,彼独婆娑其巾帻,而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独华巧其綦絇,而为不正之履。所谓“婆娑其巾帻”、“华巧其綦絇”,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是吻合朱子《家
礼》的设计的。①朱熹闲居时,每天“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庙以及先圣”。②这位言官的话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朱熹门人也广泛接受这套服饰。着装的制式化,是道学团体化的强烈表示。
如说道学家刻意求新,那肯定是错的。他们所做的,实为复古——真的复古。司马光是要复原《礼记》中的衣冠制度,朱熹《家礼》又是基于司马光的《书仪》以及三礼。这套东西在宋代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如宋人沈括所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③。起码到汉末,以儒服为主体的中华衣冠都还是常见的,所以上引徐幹文中才有“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之语。宋代已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们以儒服为怪。朱熹等人所为,是要复兴久已失传的一个东西。这又是宋儒承接汉儒的地方,不同的是,宋儒要面临诧异的目光。
同样是在礼乐崩坏之时,孔子之党已经有了因衣冠不合俗而被嘲弄的先例。《礼记·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鲁哀公见孔子,先问:“夫子之服,其儒服与?”郑玄注:“哀公馆孔子,见其服与士大夫异,又与庶人不同,疑为儒服而问之。”孔颖达疏里说:“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孔子的话似乎告诉我们,他的衣冠是殷周衣冠旧制。鲁哀公不之识,以为异类。他见面不问儒行,反对古怪的儒服大起兴趣,从心理学上讲,乃由于一般人的注意力可以轻易被视觉冲击所吸引。孔子的遭遇,就是后来朱熹等人的遭遇;不同的是,孔子尚未遇到党禁。前面之所以说“孔子之党”,是因为“儒服”确是孔门通服,非孔子独服。这可从子路初“冠雄鸡、佩豭豚”,后“儒服委质”,请为孔子弟子一事①推知。
几百上千人,主张统一,着装统一,已足以令人侧目,何况其服装上不与朝廷正装同,下与百姓杂服异。越直观而具象的变动,越引人注目,如不能被接受,即生争执。对一个干政团体来说,单纯这条简直已足以取祸。然而纵有绍兴党禁的先例,道学新领袖朱熹还是坚持独特的道学着装;他有着强烈的“法服”意识②,认定服装也有服统。前面说到,朱熹落职罢祠后,有部分从游者遂“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这清晰地透露,服饰成为当时划分党内党外的标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朱熹戮力衣装形制,动机原不在制造彼我鸿沟,树旗以立门户,而是儒家制礼作乐传统下的一个具体作为。礼乐理想上须覆盖天下人,所以本于礼经的法服是要推广到从天子到庶人的所有人的。换句话说,变革朝野服色(例如,消除朝服中的胡服元素),原在理学党的政治理想之内。
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学一门在衣冠要求上极端低调,也相应地在制礼作乐这一环上表现逊色。明嘉靖至万历期间,从世宗、严嵩,到神宗、张居正,指责王阳明及其门人朋友者不一而足,却从未提到他们有“奇装异服”。这只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在服饰上就中规中矩。
考阳明门下,唯王艮颇有意于古礼。《心斋年谱》载,王艮三十七岁:“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绦绖、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这与程朱学人的做派相类,与流于放荡的泰州后学反而迥异。三十八岁:“入豫章城,服所制冠服,观者环绕市道。”后来又依孔子车制自创蒲轮,行至都下,“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④可见,与朱熹一样,王艮不惮于违俗,并因而被人视为异类。然而王艮在王门是孤独的。在豫章,阳明门人问阳明:王艮“异服者与?”阳明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将谁友?”阳明的回答说明,他了解儒家法服之事,且能包容王艮的骇俗之举。而整个对话透露,当时王门包括阳明本人都不穿古儒服(法服)。换句话说,阳明是知而不为。即使是阳明对王艮的支持,其实也有限。当王艮的“乖张”震惊京城后,阳明也坐不住了,所以才有“亦移书责之”,谓王艮“行事太奇”之事。归根结底,他是害怕带来他认为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我们知道,被贬龙场(1506年)后,阳明就刻意保持低调。①何况王艮去北京在1523年,而1522年十月刚发生过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骠请禁心学之事。阳明、心斋的年谱都提到,阳明事后裁抑王艮。但裁抑到何等程度,王艮最后有无改换服装,我们不知道。朱舜水回答日本人问明朝深衣,说:“仅见《家礼》耳。明朝如丘文庄(丘濬,1420—1495)亦尝服之,然广东远不可见。王阳明门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见。”吾妻重二猜测,朱舜水提到的王阳明门人就是王艮。②不管王艮是否坚持穿深衣,他都是极少数的特例,而且是被压抑的特例。
小中见大,阳明对儒家服制的不作为,背后是阳明学对整个儒家礼制的淡漠。阳明本人在南赣等地推行过吕氏乡约,固然是礼乐教化的一种,但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了。从学术史的角度,阳明学对礼学的贡献也的确乏善可陈。明清鼎革之际,遗民往往批评明末士风浮薄,拙于践履;特别地,在学术领域,有心性之清谈,无经世之实学。③阳明学对这些现象要负主要责任。
嘉靖大礼议是明代涉及礼乐制作的极重大事件,阳明一门对它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礼议焦点是,嘉靖帝以藩王(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则其宗庙所奉祀的“皇考”将是本生父,还是前任皇帝?换句话说,是血缘关系重要,还是继承关系重要,特别是对作为天下楷模的天子来说?依据儒家宗法,血缘不是那么重要,嘉靖帝好比过继,不应当再以本生父为尊。宋英宗与明世宗有类似情况,而且也发生过经年不息的“濮议之争”。感情上谁都更爱亲生父母,宋英宗也是坚持尊本生父,并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儒家公论无不以英宗破坏宗法为非。想不到历史重演,明世宗仍是坚持尊本生父,而且一意孤行,也取得最后胜利。然而后果是很严重的。明世宗血腥镇压反对派(以“左顺门”一案为尤),藉此愈发专断,士大夫愈发不敢有异议。《明史》即以世宗为明朝纲纪沦坏的起点:“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①
在这样攸关制度化儒家的生命的事件中,当时已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其态度如何?首先,他没有参与礼仪,在公共领域对大礼仪全程缄默。其次,据学者任文利勾稽,他私下的真实意见,与世宗及世宗支持者一致。②这样的态度,固然与阳明相对偏向人情的哲学有关(世宗尊本生父的理由,就是孝子的自然之情)。这里,理论上可对他的缄默做两种理解,一是纯粹不想惹麻烦,二是变相支持世宗的主张。根据我们对阳明的整体把握,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若然,那就是对儒家典章实际运用的极端不作为。然而就算是第二种(其实几乎不可能),等于他有意借世宗之手调整儒家礼制,是一种积极作为,那么至少从后果来看,也是很有问题的。章太炎评价:
大礼议起,文成(王守仁)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③
责备不可谓不严。④儒学不反对变革礼乐,只是如《中庸》所言,此事惟许之“圣王”。阳明门下的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是不是佞臣,且不论,但主导礼仪的张璁、桂萼,无疑是奉承希旨之辈。特别地,世宗本人的专断,快意刑诛,中年后的耽于仙术,绝是事实。无论世宗还是他的执政集团都够不上“圣王”资格,而阳明却把制礼作乐的权柄完全交给了他们,以致祸患无穷。
阳明小心翼翼地避免冲撞现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总结起来,朱子之政党是努力复兴礼乐,即在衣装细节上也不惜抵牾权力集团及社会习俗的惯常审美;王子之社团是努力回避礼乐,即在衣装细节上也不敢与人不同。王学少招嫌,少被讥,不亦宜乎?外在行为中规中矩,减少社会及政治的异样目光,能达到保护自由讲学的目的。既如此,自然就不是建党干政这一路。
问题是,没办法或不愿意结党的阳明一派为何最后仍被打击?简单说,是因为唐甄说的“聚众讲学,其始虽无党心,其渐必成党势”①。各种资料都显示,王门的讲学规模胜过宋儒。这样的话,即使全然在野,终将发展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何况其中本有大量士子与朝廷命官。如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就是嘉靖末隆庆初讲学大盛的第一推手。单论团体纯粹在基层膨胀,从而引起政权警惕,阳明后学中也有迹可寻。那就是泰州门下的颜山农一脉。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载:
嘉隆之际,讲学之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阳明)之变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这段批评的话透露的一个事实是,颜山农的讲学活动已经“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弦外之音是,易引发自下而上的动乱。这是儒家发展出的民间宗教新模式,虽然还是社团,却是令当政者害怕的特殊社团,其颠覆政权的风险比政坛朋党有过之无不及。颜山农终因行事“张皇”,被政客以他事下狱。②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下令禁学,毁天下书院,“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颜山农门人何心隐也是在此间被捕,死于狱中。③尽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王守仁,想必没有料到这些结局。
宋代反道学者攻击道学时,往往提到道学者独特的着装——宽衣、博带、缁冠、幅巾、黑履等等——也就是朱熹《家礼》力图复活的周礼“深衣”制度。南宋初年言者称伊川之徒“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可见朱熹之前的道学群体已因服饰之故而被当成另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司马温公依《礼记》做深衣、冠簪、幅巾、缙带。”②这些为朱熹所直接继承。但他继承程颐多少,则有疑问。古代服饰中确有名“程子巾”(实为冠)者,但程颐是否推广过格外醒目的幅巾,尚无更多史料可资佐证。至于朱熹,则毫无疑问为道学人士设计了十分独特的服饰。《道命录》卷七下“言者论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载一位言官的反感之语:
臣闻此徒盛炽之时,宽衣博带,高谈阔论,或沉默不言,则其口似瘖,或蹁跹不趋,则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时,儒者事也,彼独婆娑其巾帻,而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独华巧其綦絇,而为不正之履。所谓“婆娑其巾帻”、“华巧其綦絇”,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是吻合朱子《家
礼》的设计的。①朱熹闲居时,每天“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庙以及先圣”。②这位言官的话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朱熹门人也广泛接受这套服饰。着装的制式化,是道学团体化的强烈表示。
如说道学家刻意求新,那肯定是错的。他们所做的,实为复古——真的复古。司马光是要复原《礼记》中的衣冠制度,朱熹《家礼》又是基于司马光的《书仪》以及三礼。这套东西在宋代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如宋人沈括所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③。起码到汉末,以儒服为主体的中华衣冠都还是常见的,所以上引徐幹文中才有“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之语。宋代已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们以儒服为怪。朱熹等人所为,是要复兴久已失传的一个东西。这又是宋儒承接汉儒的地方,不同的是,宋儒要面临诧异的目光。
同样是在礼乐崩坏之时,孔子之党已经有了因衣冠不合俗而被嘲弄的先例。《礼记·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鲁哀公见孔子,先问:“夫子之服,其儒服与?”郑玄注:“哀公馆孔子,见其服与士大夫异,又与庶人不同,疑为儒服而问之。”孔颖达疏里说:“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孔子的话似乎告诉我们,他的衣冠是殷周衣冠旧制。鲁哀公不之识,以为异类。他见面不问儒行,反对古怪的儒服大起兴趣,从心理学上讲,乃由于一般人的注意力可以轻易被视觉冲击所吸引。孔子的遭遇,就是后来朱熹等人的遭遇;不同的是,孔子尚未遇到党禁。前面之所以说“孔子之党”,是因为“儒服”确是孔门通服,非孔子独服。这可从子路初“冠雄鸡、佩豭豚”,后“儒服委质”,请为孔子弟子一事①推知。
几百上千人,主张统一,着装统一,已足以令人侧目,何况其服装上不与朝廷正装同,下与百姓杂服异。越直观而具象的变动,越引人注目,如不能被接受,即生争执。对一个干政团体来说,单纯这条简直已足以取祸。然而纵有绍兴党禁的先例,道学新领袖朱熹还是坚持独特的道学着装;他有着强烈的“法服”意识②,认定服装也有服统。前面说到,朱熹落职罢祠后,有部分从游者遂“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这清晰地透露,服饰成为当时划分党内党外的标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朱熹戮力衣装形制,动机原不在制造彼我鸿沟,树旗以立门户,而是儒家制礼作乐传统下的一个具体作为。礼乐理想上须覆盖天下人,所以本于礼经的法服是要推广到从天子到庶人的所有人的。换句话说,变革朝野服色(例如,消除朝服中的胡服元素),原在理学党的政治理想之内。
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学一门在衣冠要求上极端低调,也相应地在制礼作乐这一环上表现逊色。明嘉靖至万历期间,从世宗、严嵩,到神宗、张居正,指责王阳明及其门人朋友者不一而足,却从未提到他们有“奇装异服”。这只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在服饰上就中规中矩。
考阳明门下,唯王艮颇有意于古礼。《心斋年谱》载,王艮三十七岁:“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绦绖、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这与程朱学人的做派相类,与流于放荡的泰州后学反而迥异。三十八岁:“入豫章城,服所制冠服,观者环绕市道。”后来又依孔子车制自创蒲轮,行至都下,“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④可见,与朱熹一样,王艮不惮于违俗,并因而被人视为异类。然而王艮在王门是孤独的。在豫章,阳明门人问阳明:王艮“异服者与?”阳明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将谁友?”阳明的回答说明,他了解儒家法服之事,且能包容王艮的骇俗之举。而整个对话透露,当时王门包括阳明本人都不穿古儒服(法服)。换句话说,阳明是知而不为。即使是阳明对王艮的支持,其实也有限。当王艮的“乖张”震惊京城后,阳明也坐不住了,所以才有“亦移书责之”,谓王艮“行事太奇”之事。归根结底,他是害怕带来他认为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我们知道,被贬龙场(1506年)后,阳明就刻意保持低调。①何况王艮去北京在1523年,而1522年十月刚发生过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骠请禁心学之事。阳明、心斋的年谱都提到,阳明事后裁抑王艮。但裁抑到何等程度,王艮最后有无改换服装,我们不知道。朱舜水回答日本人问明朝深衣,说:“仅见《家礼》耳。明朝如丘文庄(丘濬,1420—1495)亦尝服之,然广东远不可见。王阳明门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见。”吾妻重二猜测,朱舜水提到的王阳明门人就是王艮。②不管王艮是否坚持穿深衣,他都是极少数的特例,而且是被压抑的特例。
小中见大,阳明对儒家服制的不作为,背后是阳明学对整个儒家礼制的淡漠。阳明本人在南赣等地推行过吕氏乡约,固然是礼乐教化的一种,但此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了。从学术史的角度,阳明学对礼学的贡献也的确乏善可陈。明清鼎革之际,遗民往往批评明末士风浮薄,拙于践履;特别地,在学术领域,有心性之清谈,无经世之实学。③阳明学对这些现象要负主要责任。
嘉靖大礼议是明代涉及礼乐制作的极重大事件,阳明一门对它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礼议焦点是,嘉靖帝以藩王(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则其宗庙所奉祀的“皇考”将是本生父,还是前任皇帝?换句话说,是血缘关系重要,还是继承关系重要,特别是对作为天下楷模的天子来说?依据儒家宗法,血缘不是那么重要,嘉靖帝好比过继,不应当再以本生父为尊。宋英宗与明世宗有类似情况,而且也发生过经年不息的“濮议之争”。感情上谁都更爱亲生父母,宋英宗也是坚持尊本生父,并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儒家公论无不以英宗破坏宗法为非。想不到历史重演,明世宗仍是坚持尊本生父,而且一意孤行,也取得最后胜利。然而后果是很严重的。明世宗血腥镇压反对派(以“左顺门”一案为尤),藉此愈发专断,士大夫愈发不敢有异议。《明史》即以世宗为明朝纲纪沦坏的起点:“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①
在这样攸关制度化儒家的生命的事件中,当时已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其态度如何?首先,他没有参与礼仪,在公共领域对大礼仪全程缄默。其次,据学者任文利勾稽,他私下的真实意见,与世宗及世宗支持者一致。②这样的态度,固然与阳明相对偏向人情的哲学有关(世宗尊本生父的理由,就是孝子的自然之情)。这里,理论上可对他的缄默做两种理解,一是纯粹不想惹麻烦,二是变相支持世宗的主张。根据我们对阳明的整体把握,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若然,那就是对儒家典章实际运用的极端不作为。然而就算是第二种(其实几乎不可能),等于他有意借世宗之手调整儒家礼制,是一种积极作为,那么至少从后果来看,也是很有问题的。章太炎评价:
大礼议起,文成(王守仁)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③
责备不可谓不严。④儒学不反对变革礼乐,只是如《中庸》所言,此事惟许之“圣王”。阳明门下的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是不是佞臣,且不论,但主导礼仪的张璁、桂萼,无疑是奉承希旨之辈。特别地,世宗本人的专断,快意刑诛,中年后的耽于仙术,绝是事实。无论世宗还是他的执政集团都够不上“圣王”资格,而阳明却把制礼作乐的权柄完全交给了他们,以致祸患无穷。
阳明小心翼翼地避免冲撞现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总结起来,朱子之政党是努力复兴礼乐,即在衣装细节上也不惜抵牾权力集团及社会习俗的惯常审美;王子之社团是努力回避礼乐,即在衣装细节上也不敢与人不同。王学少招嫌,少被讥,不亦宜乎?外在行为中规中矩,减少社会及政治的异样目光,能达到保护自由讲学的目的。既如此,自然就不是建党干政这一路。
问题是,没办法或不愿意结党的阳明一派为何最后仍被打击?简单说,是因为唐甄说的“聚众讲学,其始虽无党心,其渐必成党势”①。各种资料都显示,王门的讲学规模胜过宋儒。这样的话,即使全然在野,终将发展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何况其中本有大量士子与朝廷命官。如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就是嘉靖末隆庆初讲学大盛的第一推手。单论团体纯粹在基层膨胀,从而引起政权警惕,阳明后学中也有迹可寻。那就是泰州门下的颜山农一脉。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载:
嘉隆之际,讲学之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阳明)之变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这段批评的话透露的一个事实是,颜山农的讲学活动已经“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弦外之音是,易引发自下而上的动乱。这是儒家发展出的民间宗教新模式,虽然还是社团,却是令当政者害怕的特殊社团,其颠覆政权的风险比政坛朋党有过之无不及。颜山农终因行事“张皇”,被政客以他事下狱。②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下令禁学,毁天下书院,“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颜山农门人何心隐也是在此间被捕,死于狱中。③尽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王守仁,想必没有料到这些结局。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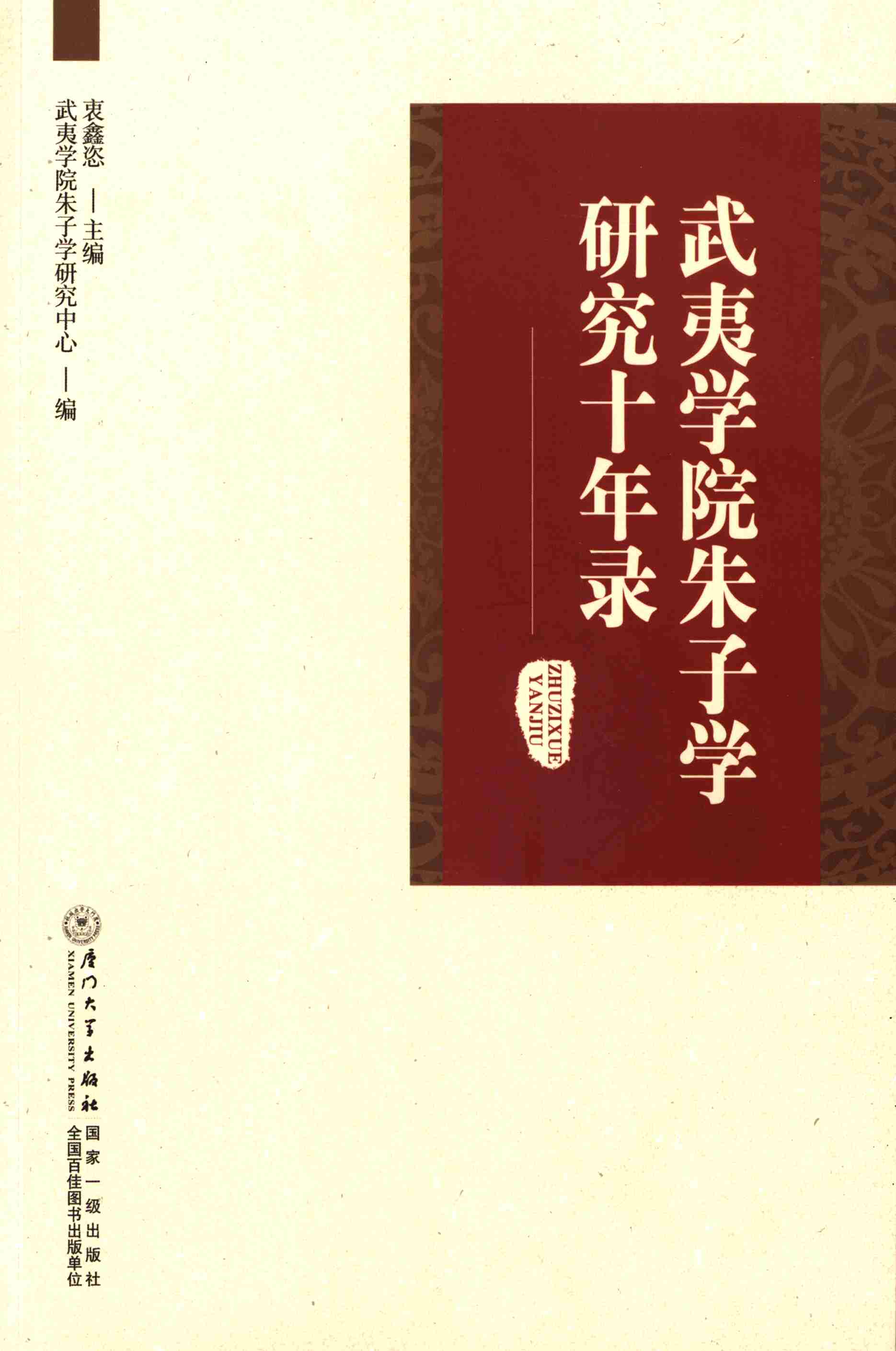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阅读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