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学的团体化传统
| 内容出处: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94 |
| 颗粒名称: | 一、道学的团体化传统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4 |
| 页码: | 127-130 |
| 摘要: |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宋明两代的三次“党锢”,揭示了士大夫集团在政治斗争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作者指出,这些被镇压的反对党,实际上是持异议的士大夫集团,他们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通过结党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利益。尽管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受到打压和限制,但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表明了他们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
| 关键词: | 政治斗争 儒家文化 朱熹 |
内容
以下是发生于宋明两代的三次“党锢”(对反对党的镇压):北宋“元佑奸党碑”,录97人;南宋庆元“伪学逆党”,籍59人;晚明天启的东林“点将录”,点108人。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政敌们制作的“党员名册”。这些“党”,都是持异议的士大夫集团,且都是理学阶段的儒士集团。
宋儒是不惮于结党的,宋代党争也于历代最频繁。欧阳修作《朋党论》,从儒家义理系统出发,论证君子有党,是宋代士大夫党派政治的宣言。朱熹对此有充分的自觉,屡称“吾党”,①宣扬“以吾党致力于吾道”。朱子不是不知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②,然而“无党”犹如“大同”,是一种理想,在君子小人杂处的现实政治中,择友与站队是难免的。因此朱子严厉斥责无条件的无党论:“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言‘无党’,是大乱之道。”③
东汉与两宋都是养士(培养优容士大夫)的美好时光,士大夫之交游与互相标榜也相当一致。史家述桓灵党锢前的东汉交游之盛:
前太尉黄琼(86—164)之卒也,四方名士来会其葬者六七千人。郭泰(128—169)初到洛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110—169),膺与为友。后归太原乡里,诸儒送之河上,车数千辆,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168)、王畅(?—169)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抑,屣履到门。
朱熹之世,与此相近。如会葬,王懋竑《朱子年谱》“庆元六年(1200年)冬十月壬申”条:
(朱熹)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会葬者几千人。
此事发生在党禁之恐怖气氛中。此前,当朱熹之卒,尚有言者奏言“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陈荣捷《朱子门人》统计亲炙者有629人。会葬者既大逸此数,且并非所有门人皆到,可知朱子的影响不是“学术小圈子”一语能够概括。又如太学生之与名士结为共同体,有孙逢吉之例媲美之。绍熙二年(1191年),孙逢吉(庆元党锢中曾论救朱熹)论劾结交近幸的官僚,光宗不从,他坚决求去,离开临安时,“两学之士数百人出祖关外”①①。宋代太学规模不及东汉,难以动辄万人,但两学之士数百人送行因谏诤去国的孙逢吉,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态度的,意义非凡。鉴于两宋太学生参政之活跃,有理由怀疑,朱熹的会葬也有大量太学生参与。
又,庆元二年(1196年),受朱熹案牵连,蔡元定发配道州,徒步上路,朱熹“与尝所游百余人,会别萧寺”②。要知道,庆元二年、三年是党事汹涌之际。树倒猢狲散是常有的,朱熹也遇到过。他落职罢祠后,往日从游之巽懦者,有些也是“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但竟也有那么多“不散”的,甘冒风险,围在已是布衣的朱熹身边,这就是一种有别于利益共同体的信仰共同体了。所谓利益共同体,南宋的职业官僚集团就是,明末的阉党也是。当然,相比信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范畴,欧阳修依义利之辨划分的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用在这里也许更贴切;“利益共同体”与“小人之党”同义,但“信仰共同体”却不一定是“君子之党”。需要辨明的是,即使是南宋理学集团这个“君子之党”,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叶适这些君子,其成员却也不是个个君子。大量依附者,正如反对党的奏文所言,是名利之徒:说利,是因为道学也有得势之时;说名,是因为道学家本以道德为标榜,以名为重。这些投机分子的存在,也与东汉类似。汉末徐幹《中论》卷下《谴交》篇谴责俗士之交: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民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于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
如清初士人多以党争为宋明灭亡之由,徐幹也有一概否定士人交结为党之意,落脚点是以党群为私利之门。其确否,兹不论,我们只想借徐幹的观察得知,郭泰、李膺等的附合者中一定也存在大量渔利之徒。实际上,投机者被大量吸引,正是党势形成的表现。反过来,投机者成批离去,则是党势不再的表现。
大体上,汉末之太学党(姑且这么叫),南宋中期之理学党,明末之东林党,最初都是由于达到了规模效应的清议行为而引发权力不安与弹压。它们自有政坛人物为之扶植,但更需要精神领袖为号召,这些领袖纯靠道德学问为魅力,政治上往往不得意。太学生领袖郭泰,终生不仕;理学之魁朱熹,立朝仅四十日;东林书院主盟顾宪成,讲学是在被革职之后。他们身在江湖,但心系天下治乱。这些精神领袖的存在,完美地演绎了儒家道尊于势的传统。郭泰时的精神动力叫做名教,标榜名节;朱熹、顾宪成时的精神动力叫做道学(或理学),标榜道德;道学未尝不是名教。这些往往由异己的政治力量逼出来的党,也不是没有“施政纲领”。统说是先王之治、三代之治;分说的话,太学党的纲领首在五经(汉儒一般相信,孔子以《春秋》为大汉立法),理学党首在四书(如《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这对应不同的理论形态:汉儒的五经政治学,立足后天经验(典章文物),是综合型的,是史学;宋儒的四书(加周易)政治学,立足先天理念(天理良知),是分析型的,是哲学。
不管怎么说,无论太学党,还是理学党,还是东林党,党诤(有党有诤)是一样的。这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都只是继承了孔子开创的私学干政模式。有人也许会说,郭泰游太学,不能称之为私学活动。殊不知,桓灵之际,太学基本上已成士族的自治领(好似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设想的那种“学校”),不受皇帝与宦官控制,于是灵帝才有光和元年(178年)的“鸿都门学”之设,以抗衡太学。其时之太学,名为官学,实为私学。孔子的言论著述,固然对后世影响巨大,但其有教无类、弟子环绕、周游弘道的生平事业,对后世儒者更是亲切的感召。一句话,宋明道学讲学成党,从整个儒学史来看,继承性毕竟是第一位的。其讲学交游、标榜品题,与东汉相当,故受禁锢也相似。只有孔子之党,因远处秦制建立之前,故未遭难。而秦制一旦建立,儒学也就迎来第一次大祸,即焚书坑儒。
宋儒是不惮于结党的,宋代党争也于历代最频繁。欧阳修作《朋党论》,从儒家义理系统出发,论证君子有党,是宋代士大夫党派政治的宣言。朱熹对此有充分的自觉,屡称“吾党”,①宣扬“以吾党致力于吾道”。朱子不是不知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②,然而“无党”犹如“大同”,是一种理想,在君子小人杂处的现实政治中,择友与站队是难免的。因此朱子严厉斥责无条件的无党论:“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言‘无党’,是大乱之道。”③
东汉与两宋都是养士(培养优容士大夫)的美好时光,士大夫之交游与互相标榜也相当一致。史家述桓灵党锢前的东汉交游之盛:
前太尉黄琼(86—164)之卒也,四方名士来会其葬者六七千人。郭泰(128—169)初到洛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110—169),膺与为友。后归太原乡里,诸儒送之河上,车数千辆,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168)、王畅(?—169)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抑,屣履到门。
朱熹之世,与此相近。如会葬,王懋竑《朱子年谱》“庆元六年(1200年)冬十月壬申”条:
(朱熹)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会葬者几千人。
此事发生在党禁之恐怖气氛中。此前,当朱熹之卒,尚有言者奏言“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陈荣捷《朱子门人》统计亲炙者有629人。会葬者既大逸此数,且并非所有门人皆到,可知朱子的影响不是“学术小圈子”一语能够概括。又如太学生之与名士结为共同体,有孙逢吉之例媲美之。绍熙二年(1191年),孙逢吉(庆元党锢中曾论救朱熹)论劾结交近幸的官僚,光宗不从,他坚决求去,离开临安时,“两学之士数百人出祖关外”①①。宋代太学规模不及东汉,难以动辄万人,但两学之士数百人送行因谏诤去国的孙逢吉,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态度的,意义非凡。鉴于两宋太学生参政之活跃,有理由怀疑,朱熹的会葬也有大量太学生参与。
又,庆元二年(1196年),受朱熹案牵连,蔡元定发配道州,徒步上路,朱熹“与尝所游百余人,会别萧寺”②。要知道,庆元二年、三年是党事汹涌之际。树倒猢狲散是常有的,朱熹也遇到过。他落职罢祠后,往日从游之巽懦者,有些也是“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③。但竟也有那么多“不散”的,甘冒风险,围在已是布衣的朱熹身边,这就是一种有别于利益共同体的信仰共同体了。所谓利益共同体,南宋的职业官僚集团就是,明末的阉党也是。当然,相比信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范畴,欧阳修依义利之辨划分的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用在这里也许更贴切;“利益共同体”与“小人之党”同义,但“信仰共同体”却不一定是“君子之党”。需要辨明的是,即使是南宋理学集团这个“君子之党”,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叶适这些君子,其成员却也不是个个君子。大量依附者,正如反对党的奏文所言,是名利之徒:说利,是因为道学也有得势之时;说名,是因为道学家本以道德为标榜,以名为重。这些投机分子的存在,也与东汉类似。汉末徐幹《中论》卷下《谴交》篇谴责俗士之交: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民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于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
如清初士人多以党争为宋明灭亡之由,徐幹也有一概否定士人交结为党之意,落脚点是以党群为私利之门。其确否,兹不论,我们只想借徐幹的观察得知,郭泰、李膺等的附合者中一定也存在大量渔利之徒。实际上,投机者被大量吸引,正是党势形成的表现。反过来,投机者成批离去,则是党势不再的表现。
大体上,汉末之太学党(姑且这么叫),南宋中期之理学党,明末之东林党,最初都是由于达到了规模效应的清议行为而引发权力不安与弹压。它们自有政坛人物为之扶植,但更需要精神领袖为号召,这些领袖纯靠道德学问为魅力,政治上往往不得意。太学生领袖郭泰,终生不仕;理学之魁朱熹,立朝仅四十日;东林书院主盟顾宪成,讲学是在被革职之后。他们身在江湖,但心系天下治乱。这些精神领袖的存在,完美地演绎了儒家道尊于势的传统。郭泰时的精神动力叫做名教,标榜名节;朱熹、顾宪成时的精神动力叫做道学(或理学),标榜道德;道学未尝不是名教。这些往往由异己的政治力量逼出来的党,也不是没有“施政纲领”。统说是先王之治、三代之治;分说的话,太学党的纲领首在五经(汉儒一般相信,孔子以《春秋》为大汉立法),理学党首在四书(如《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这对应不同的理论形态:汉儒的五经政治学,立足后天经验(典章文物),是综合型的,是史学;宋儒的四书(加周易)政治学,立足先天理念(天理良知),是分析型的,是哲学。
不管怎么说,无论太学党,还是理学党,还是东林党,党诤(有党有诤)是一样的。这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都只是继承了孔子开创的私学干政模式。有人也许会说,郭泰游太学,不能称之为私学活动。殊不知,桓灵之际,太学基本上已成士族的自治领(好似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设想的那种“学校”),不受皇帝与宦官控制,于是灵帝才有光和元年(178年)的“鸿都门学”之设,以抗衡太学。其时之太学,名为官学,实为私学。孔子的言论著述,固然对后世影响巨大,但其有教无类、弟子环绕、周游弘道的生平事业,对后世儒者更是亲切的感召。一句话,宋明道学讲学成党,从整个儒学史来看,继承性毕竟是第一位的。其讲学交游、标榜品题,与东汉相当,故受禁锢也相似。只有孔子之党,因远处秦制建立之前,故未遭难。而秦制一旦建立,儒学也就迎来第一次大祸,即焚书坑儒。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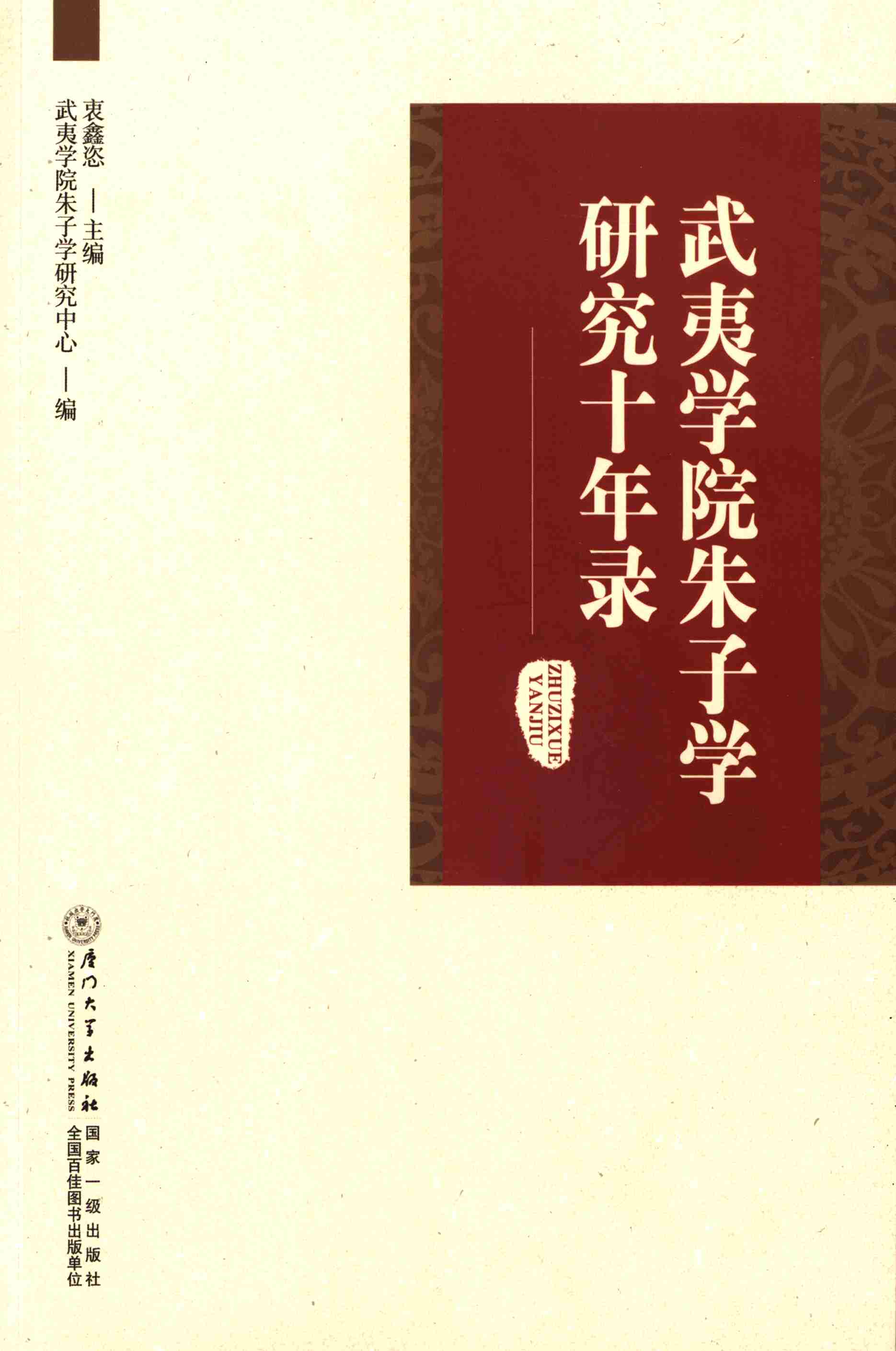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阅读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