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命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84 |
| 颗粒名称: | 一、天命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35-14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陈淳认为天命体现在日用之间,强调天理自然而非人力所安排。他将道纳入天命,指出道乃天理自然,为天命所定,在日用人伦万事间均有体现。同时,他讨论了天命的真诚无妄,强调其自然性与非人为性。 |
| 关键词: | 陈淳 命 根原 |
内容
在陈淳看来,在日用之间,事事均体现天命。庆元六年(1200),与廖子晦的书信中,陈淳言道:
大抵许多合做底道理,散在事物而总会于吾心,离心而论事,则事无本;离事而论理,则理为虚。须于人心之中,日用事物之际,见得所合做底,便只是此理,一一有去处,乃为实见。所合做底做得恰好,乃为实践。即此实见无复差迷,便是择善;即此实践更能耐久,便是固执。即此所合做底分来,便成中正仁义。即此所合做底见定浅深轻重,便是日用枝叶,即此所合做底浅深轻重,元有自然条理缝罅,非由人力安排,便是天命根原。
用天理(命)统摄道,指出此理、此道贯穿于人心,体现于日用事物之际。强调天命乃天理自然非人力所安排。
嘉定十年(1217),其在严陵讲学,作《道学体统》言道:
盖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
其将道纳入天命,指出道乃天理自然,为天命所定,在日用人伦万事间均有体现。即是说,人生中日用人伦万事所遵行的道,究其根源乃是天命。诚如学者所指出:“在这个概括中,陈淳清楚地用‘理’将心(性与情之统合)、身(自然生理与社会关系之统合)、行(个人行为与社会责任、日用琐事与家国大事之统合)统串为一体,使朱熹哲学呈现出结构完整而有机、层次清晰而相因的面相。”
陈淳认为,天道真诚无妄。其言曰:“盖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诚者天之道’是也。”因而,其讨论天命时,尤为强调其自然性与非人为性。
在这两段话中,陈淳不仅讨论天命的形而上含义,而且突出其在人事中的体现。可谓沿袭朱熹论命时重人事的倾向。
(一)理命、气命
朱熹以降、诰敕阐释命,然天无言,如何命令人呢?对此,陈淳解释道:“天岂‘谆谆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又曰:“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在理气化育万物的过程中,天便将命赋予万物包括人。当气到某物生某物时,天便赋予了万事万物这个理。即是说,天通过气赋予万事万物包括人,强调了气的作用。总之,天之命于万事万物,是在气化流行的过程中实现,并未有一个超乎理气之外的命令者。可见,其亦强调命为天所赋予,强调气化流行的过程。
陈淳曾问朱熹道:“‘命’字有专以理言者,有专以气言者。”朱熹答曰:“也都相离不得。盖天非气,无以命于人;人非气,无以受天所命。”提点其不可分割看待理命、气命,强调理气不相离,理命与气命本质为一个命,并指出气的中介性质。
基于此,陈淳亦就理、气两个层面讨论命。其言曰:
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
理不外乎气。在其看来,理为中枢枢纽,但言理不可离气。理之所以存在,乃是阴阳二气流行化育,其上需要一个主宰,于是便在气上指出一个理。可见,在他所论之理气关系中,气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朱熹明显不同。由此出发,其更重视讨论气命。其言道:
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一般说贫富贵贱、夭寿祸福,如所谓“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是说人之智愚贤否。
就气命而言,亦有两个方面:一以气之短长、厚薄差异上言为命分,如寿夭、生死、祸福、贫贱、富贵等均为其所定,此为通常所言之命运;一以气之清浊上言,如人之贤否、智愚即为其所定。其又言道:“若就人品类论,则上天所赋皆一般,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其将所值纳入气禀的讨论中,指出天赋与时,乃一视同仁、毫无二致,但因个体所值(所遇)不同,因而气禀才有清浊、厚薄之差异。朱熹论所值、所禀时,其所言之“气数”实有所值之意。在此,陈淳明确用所值代替气数,可谓抓住要领。
在此基础上,陈淳详论所值对个体气禀之影响,进而讨论气禀对寿夭及人品高低、贤愚等之影响,并评价古今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陈淳从气禀之清浊与气禀赋质之杂粹两个层面探讨。
首先,陈淳认为:“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其以尧、舜为例,二圣得气至清至粹,所以聪明神圣;得气清高而禀厚,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得气最长,所以享国皆百余岁。这是在天地之气至清至极的时代,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天地大气已经衰微,同为圣人的孔子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天地大气已衰,孔夫子虽有至清至粹之气,有生知之智力,但气禀不高不厚,只能不为所用、周游列国,所得之气又不甚长,只得70余岁的中寿。颜回气禀亦是清明纯粹,仅次于圣人,但气不足,因而早夭而亡。
其次,“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理义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人好比银盏子,禀受之理义即为盏底的银花子,气禀如同银盏子中盛的水。水之清浊决定盏底的银花子能否看得分明,气禀之清浊则决定理义是否被遮蔽,从而决定人之贤愚。因此,其言道:
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
贤人气禀清多浊少,浊气不能遮蔽其理义,因而智慧才智易开发。大贤以下之人,禀得浊气、清气参半,甚或浊气更多,其理义被遮蔽得较为严重,难以显现。若要驱除遮蔽,必须加以十分澄治之功。如果能够力学,亦能变化气质之性,转昏为明。尽管气命已前定人之贤愚,但是通过澄治之功,亦可转愚为贤。是知,贤愚虽为天命所定,但可通过人之主观能动性改变。与朱熹一样,陈淳亦肯定人能克服气禀清浊的限制,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改变前定的贤否智愚之别,追求圣贤的至清至粹的境界。
其又言道:
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之不笃,不能承载得道理,多杂诡谲去,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裹面,亦透底清彻。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煎白水则成赤汤,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比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了,终不透莹。
还有一些人,气禀清明,但是天赋资质不粹。虽然能尽看得出义理,却不能笃行之。如同银盏子盛了清澈的泉水,盏底银花子完全看得分明;但是泉源不净,泉水味道不甘醇,不能用以饮食。又有一些人,天赋资质纯粹,但是气禀不清。虽然行为举止纯正合义理,却无法体贴义理。如同银盏子盛了甘甜味美的泉水,却夹杂泥土,终不能看分明盏底的银花子。是知,人之贤愚,除受气命影响外,亦与天赋资质相关。在其看来,司马光“恭俭力行,笃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资质,只缘少那至清之气,识见不高明”,即为第二种人。因而,二程屡用理义引导他,他却一向偏执固滞,不受启发。
陈淳指出,还有一些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冲拗了。如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及或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帖顺去,反成险恶之流”。这种人虽然禀受清气,却被一股戾气所冲,因而固执己见,执拗不化。如同泉源清澈,却被另一条水流冲破,掺杂在一起,或像是中途遭遇岩石,被横截冲击,清流反成而恶流。
最后,陈淳总结道:“看来人生气禀是有多少般样,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不可以一律齐。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人之气禀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而清明之气与纯粹之赋质毕竟难以同时兼得,因而圣贤少、愚不肖者多。
陈淳以水比喻气,以肉眼可见的清澈与否比喻气禀之清浊,以水之成分比喻气禀之赋质杂粹。将气禀成分的杂与粹纳入到人之贤愚的讨论中,而不仅仅停留在清浊层面上。可以说,陈淳所论气禀清浊可以分为表面与本质两个层面。其以水喻气,形象地展现了两个层面对人之贤愚的影响。增加气禀赋质的讨论,可谓陈淳气命说的一个新说。
(二)天、命、理之别
二程认为天、命、理、性等本质为一,朱熹则认为此四者即同又异,侧重点不同。陈淳祖述师说,并一步延伸阐发。
首先,陈淳亦讲天即理。其详论道:
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
理即是天,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讲“苍苍”,是就天之体言,即是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即天道。
此外,二程认为循性曰道。朱熹则认为“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即是说命与道亦是即同又异。陈淳继承朱熹之说,言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事物从始至终之理为天道;此天道气化流行赋予万物,即为天命。此语可理解为,以理言之谓为天道,自人、物言之谓为天命,指出天道与天命是同一对象在不同角度上的指称,并用天道替代了朱熹之“天”。其仔细分析道:“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就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时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
其次,陈淳认为天与命略有区别。《孟子》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熹注曰:“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一而已。”有人问:“此处何以见二者之辨?”陈淳答曰:
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封此而反之,非人所为便是天。至以吉凶祸福地头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对此而反之,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谓之天”,是专就天之正面训义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谓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见。故吉凶祸福自天来,到于人然后为命。乃是于天理中,截断命为一边,而言其指归尔。若只就天一边说,吉凶祸福,未有人受来,如何见得是命?
在其看来,天与命虽只是一理,却有细微的差别。其一,天与命之相同处为非人为,自然无妄,强调非人力所为便是天。就吉凶祸福而言,因人自身行为招致者,乃是人力而非命;自然而然发生,非人力招致者才是命。其二,天以全体言,命则以妙用言。命乃天所赋予,但必须人禀受之后,才能见得命。强调命为人禀受所得,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再次,陈淳亦讲性即理、性命非二物。其言道: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谓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谓之礼;得天命之利,在我谓之义;得天命之贞,在我谓之智。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
其一,性即心中之理,因而性即理。元亨利贞四德之理,在人心即为仁义礼智。之所以称性,而不称理,乃是强调此理乃人心禀受于天而为我所有,强调其禀受性。其二,性乃天命赋予人,因而性、命本非二物,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由此,命即理也。其又引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是知,命强调赋予义,性则侧重禀受义。
其进一步言道:“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只管分看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所以谓之命、谓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其实理不外乎气,得天地之气成这形,得天地之理成这性。”强调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开看不能区分。须从浑然一体的理中,看二者分界:命为赋予,性为禀受。又指出理气不相离,因而性、命均不能仅就理言,还需就气言。与朱熹“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的说法不同。
最后,陈淳明确地将理一分殊说导入命论。其言道:
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达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禀也,孔子与十室均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
上至圣人,下至涂人,均禀受同一个理。此理乃上帝降衷于人,即天命于人。有人问:“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齐?”既然天赋予时乃一视同仁,为何各人之命千差万别?陈淳回答道:
譬之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放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菹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
陈淳采用比喻手法进行解说,形象地指出天命毫无二致,而各人禀受所得不同,因而有千差万别之命。其一,用雨水作为比拟。同是禀受雨水,江河水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则水位暴涨;田间水道则朝盈暮涸;不同的容器受去,又有多少、污浊、清甘、臭秽之别。其二,用菜种子作为比拟,播种在不同地方,生长情况不同;收成后,作用又各种各样。之所以与这些差异,不是施雨者、播种者有意为之,而是禀受者各自禀受不同而导致。最后,又指出该现象亦是自然之理。
朱熹亦有以理一分殊的逻辑讨论命分各不相同,但并未明确地纳入讨论中。其言道:“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则又都一般。”性仅就理言,命则兼就理气而言。气禀有多寡厚薄之别,个体之命因之而千差万别。人禀受理气而生,天赋与人之理是无差别,而人禀受之气则千差万别。这决定了人之命兼具理气而论,就理言之命应是相同的,而就气言之命则千差万别。陈淳明确地用理一分殊讲述命分差异,是对乃师之说的进一步拓展。
大抵许多合做底道理,散在事物而总会于吾心,离心而论事,则事无本;离事而论理,则理为虚。须于人心之中,日用事物之际,见得所合做底,便只是此理,一一有去处,乃为实见。所合做底做得恰好,乃为实践。即此实见无复差迷,便是择善;即此实践更能耐久,便是固执。即此所合做底分来,便成中正仁义。即此所合做底见定浅深轻重,便是日用枝叶,即此所合做底浅深轻重,元有自然条理缝罅,非由人力安排,便是天命根原。
用天理(命)统摄道,指出此理、此道贯穿于人心,体现于日用事物之际。强调天命乃天理自然非人力所安排。
嘉定十年(1217),其在严陵讲学,作《道学体统》言道:
盖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
其将道纳入天命,指出道乃天理自然,为天命所定,在日用人伦万事间均有体现。即是说,人生中日用人伦万事所遵行的道,究其根源乃是天命。诚如学者所指出:“在这个概括中,陈淳清楚地用‘理’将心(性与情之统合)、身(自然生理与社会关系之统合)、行(个人行为与社会责任、日用琐事与家国大事之统合)统串为一体,使朱熹哲学呈现出结构完整而有机、层次清晰而相因的面相。”
陈淳认为,天道真诚无妄。其言曰:“盖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诚者天之道’是也。”因而,其讨论天命时,尤为强调其自然性与非人为性。
在这两段话中,陈淳不仅讨论天命的形而上含义,而且突出其在人事中的体现。可谓沿袭朱熹论命时重人事的倾向。
(一)理命、气命
朱熹以降、诰敕阐释命,然天无言,如何命令人呢?对此,陈淳解释道:“天岂‘谆谆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又曰:“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在理气化育万物的过程中,天便将命赋予万物包括人。当气到某物生某物时,天便赋予了万事万物这个理。即是说,天通过气赋予万事万物包括人,强调了气的作用。总之,天之命于万事万物,是在气化流行的过程中实现,并未有一个超乎理气之外的命令者。可见,其亦强调命为天所赋予,强调气化流行的过程。
陈淳曾问朱熹道:“‘命’字有专以理言者,有专以气言者。”朱熹答曰:“也都相离不得。盖天非气,无以命于人;人非气,无以受天所命。”提点其不可分割看待理命、气命,强调理气不相离,理命与气命本质为一个命,并指出气的中介性质。
基于此,陈淳亦就理、气两个层面讨论命。其言曰:
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盖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个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所谓以理言者,非有离乎气,只是就气上指出个理,不杂乎气而为言耳。
理不外乎气。在其看来,理为中枢枢纽,但言理不可离气。理之所以存在,乃是阴阳二气流行化育,其上需要一个主宰,于是便在气上指出一个理。可见,在他所论之理气关系中,气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朱熹明显不同。由此出发,其更重视讨论气命。其言道:
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一般说贫富贵贱、夭寿祸福,如所谓“死生有命”与“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是说人之智愚贤否。
就气命而言,亦有两个方面:一以气之短长、厚薄差异上言为命分,如寿夭、生死、祸福、贫贱、富贵等均为其所定,此为通常所言之命运;一以气之清浊上言,如人之贤否、智愚即为其所定。其又言道:“若就人品类论,则上天所赋皆一般,而人随其所值,又各有清浊、厚薄之不齐。”其将所值纳入气禀的讨论中,指出天赋与时,乃一视同仁、毫无二致,但因个体所值(所遇)不同,因而气禀才有清浊、厚薄之差异。朱熹论所值、所禀时,其所言之“气数”实有所值之意。在此,陈淳明确用所值代替气数,可谓抓住要领。
在此基础上,陈淳详论所值对个体气禀之影响,进而讨论气禀对寿夭及人品高低、贤愚等之影响,并评价古今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陈淳从气禀之清浊与气禀赋质之杂粹两个层面探讨。
首先,陈淳认为:“圣人得气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赋质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其以尧、舜为例,二圣得气至清至粹,所以聪明神圣;得气清高而禀厚,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得气最长,所以享国皆百余岁。这是在天地之气至清至极的时代,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天地大气已经衰微,同为圣人的孔子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天地大气已衰,孔夫子虽有至清至粹之气,有生知之智力,但气禀不高不厚,只能不为所用、周游列国,所得之气又不甚长,只得70余岁的中寿。颜回气禀亦是清明纯粹,仅次于圣人,但气不足,因而早夭而亡。
其次,“大抵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理义便呈露昭著。如银盏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人好比银盏子,禀受之理义即为盏底的银花子,气禀如同银盏子中盛的水。水之清浊决定盏底的银花子能否看得分明,气禀之清浊则决定理义是否被遮蔽,从而决定人之贤愚。因此,其言道:
贤人得清气多而浊气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聪明也易开发。自大贤而下,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学,也解变化气质,转昏为明。
贤人气禀清多浊少,浊气不能遮蔽其理义,因而智慧才智易开发。大贤以下之人,禀得浊气、清气参半,甚或浊气更多,其理义被遮蔽得较为严重,难以显现。若要驱除遮蔽,必须加以十分澄治之功。如果能够力学,亦能变化气质之性,转昏为明。尽管气命已前定人之贤愚,但是通过澄治之功,亦可转愚为贤。是知,贤愚虽为天命所定,但可通过人之主观能动性改变。与朱熹一样,陈淳亦肯定人能克服气禀清浊的限制,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改变前定的贤否智愚之别,追求圣贤的至清至粹的境界。
其又言道:
有一般人,禀气清明,于义理上尽看得出,而行之不笃,不能承载得道理,多杂诡谲去,是又赋质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贮在银盏裹面,亦透底清彻。但泉脉从淤土恶木根中穿过来,味不纯甘,以之煮白米则成赤饭,煎白水则成赤汤,烹茶则酸涩,是有恶味夹杂了。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是又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比如井泉脉味纯甘绝佳,而有泥土浑浊了,终不透莹。
还有一些人,气禀清明,但是天赋资质不粹。虽然能尽看得出义理,却不能笃行之。如同银盏子盛了清澈的泉水,盏底银花子完全看得分明;但是泉源不净,泉水味道不甘醇,不能用以饮食。又有一些人,天赋资质纯粹,但是气禀不清。虽然行为举止纯正合义理,却无法体贴义理。如同银盏子盛了甘甜味美的泉水,却夹杂泥土,终不能看分明盏底的银花子。是知,人之贤愚,除受气命影响外,亦与天赋资质相关。在其看来,司马光“恭俭力行,笃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资质,只缘少那至清之气,识见不高明”,即为第二种人。因而,二程屡用理义引导他,他却一向偏执固滞,不受启发。
陈淳指出,还有一些人,“甚好说道理,只是执拗,自立一家意见,是禀气清中被一条戾气冲拗了。如泉脉出来甚清,却被一条别水横冲破了,及或遭巉岩石头横截冲激,不帖顺去,反成险恶之流”。这种人虽然禀受清气,却被一股戾气所冲,因而固执己见,执拗不化。如同泉源清澈,却被另一条水流冲破,掺杂在一起,或像是中途遭遇岩石,被横截冲击,清流反成而恶流。
最后,陈淳总结道:“看来人生气禀是有多少般样,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不可以一律齐。毕竟清明纯粹恰好底极为难得,所以圣贤少而愚不肖者多。”人之气禀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而清明之气与纯粹之赋质毕竟难以同时兼得,因而圣贤少、愚不肖者多。
陈淳以水比喻气,以肉眼可见的清澈与否比喻气禀之清浊,以水之成分比喻气禀之赋质杂粹。将气禀成分的杂与粹纳入到人之贤愚的讨论中,而不仅仅停留在清浊层面上。可以说,陈淳所论气禀清浊可以分为表面与本质两个层面。其以水喻气,形象地展现了两个层面对人之贤愚的影响。增加气禀赋质的讨论,可谓陈淳气命说的一个新说。
(二)天、命、理之别
二程认为天、命、理、性等本质为一,朱熹则认为此四者即同又异,侧重点不同。陈淳祖述师说,并一步延伸阐发。
首先,陈淳亦讲天即理。其详论道:
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
理即是天,是主宰一切的上帝。讲“苍苍”,是就天之体言,即是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即天道。
此外,二程认为循性曰道。朱熹则认为“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即是说命与道亦是即同又异。陈淳继承朱熹之说,言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贞之理而言,则谓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而赋予于物者而言,则谓之天命。”事物从始至终之理为天道;此天道气化流行赋予万物,即为天命。此语可理解为,以理言之谓为天道,自人、物言之谓为天命,指出天道与天命是同一对象在不同角度上的指称,并用天道替代了朱熹之“天”。其仔细分析道:“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论也得。就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时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
其次,陈淳认为天与命略有区别。《孟子》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熹注曰:“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一而已。”有人问:“此处何以见二者之辨?”陈淳答曰:
天与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封此而反之,非人所为便是天。至以吉凶祸福地头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对此而反之,非人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谓之天”,是专就天之正面训义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谓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见。故吉凶祸福自天来,到于人然后为命。乃是于天理中,截断命为一边,而言其指归尔。若只就天一边说,吉凶祸福,未有人受来,如何见得是命?
在其看来,天与命虽只是一理,却有细微的差别。其一,天与命之相同处为非人为,自然无妄,强调非人力所为便是天。就吉凶祸福而言,因人自身行为招致者,乃是人力而非命;自然而然发生,非人力招致者才是命。其二,天以全体言,命则以妙用言。命乃天所赋予,但必须人禀受之后,才能见得命。强调命为人禀受所得,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再次,陈淳亦讲性即理、性命非二物。其言道: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谓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谓之礼;得天命之利,在我谓之义;得天命之贞,在我谓之智。性与命本非二物,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
其一,性即心中之理,因而性即理。元亨利贞四德之理,在人心即为仁义礼智。之所以称性,而不称理,乃是强调此理乃人心禀受于天而为我所有,强调其禀受性。其二,性乃天命赋予人,因而性、命本非二物,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由此,命即理也。其又引程子曰:“天所付为命,人所受为性。”是知,命强调赋予义,性则侧重禀受义。
其进一步言道:“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看则不分晓。只管分看不合看,又离了,不相干涉。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所以谓之命、谓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个理,须有个形骸方载得此理。其实理不外乎气,得天地之气成这形,得天地之理成这性。”强调性命只是一个道理,不分开看不能区分。须从浑然一体的理中,看二者分界:命为赋予,性为禀受。又指出理气不相离,因而性、命均不能仅就理言,还需就气言。与朱熹“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的说法不同。
最后,陈淳明确地将理一分殊说导入命论。其言道:
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达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禀也,孔子与十室均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
上至圣人,下至涂人,均禀受同一个理。此理乃上帝降衷于人,即天命于人。有人问:“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齐?”既然天赋予时乃一视同仁,为何各人之命千差万别?陈淳回答道:
譬之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放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菹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
陈淳采用比喻手法进行解说,形象地指出天命毫无二致,而各人禀受所得不同,因而有千差万别之命。其一,用雨水作为比拟。同是禀受雨水,江河水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则水位暴涨;田间水道则朝盈暮涸;不同的容器受去,又有多少、污浊、清甘、臭秽之别。其二,用菜种子作为比拟,播种在不同地方,生长情况不同;收成后,作用又各种各样。之所以与这些差异,不是施雨者、播种者有意为之,而是禀受者各自禀受不同而导致。最后,又指出该现象亦是自然之理。
朱熹亦有以理一分殊的逻辑讨论命分各不相同,但并未明确地纳入讨论中。其言道:“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则又都一般。”性仅就理言,命则兼就理气而言。气禀有多寡厚薄之别,个体之命因之而千差万别。人禀受理气而生,天赋与人之理是无差别,而人禀受之气则千差万别。这决定了人之命兼具理气而论,就理言之命应是相同的,而就气言之命则千差万别。陈淳明确地用理一分殊讲述命分差异,是对乃师之说的进一步拓展。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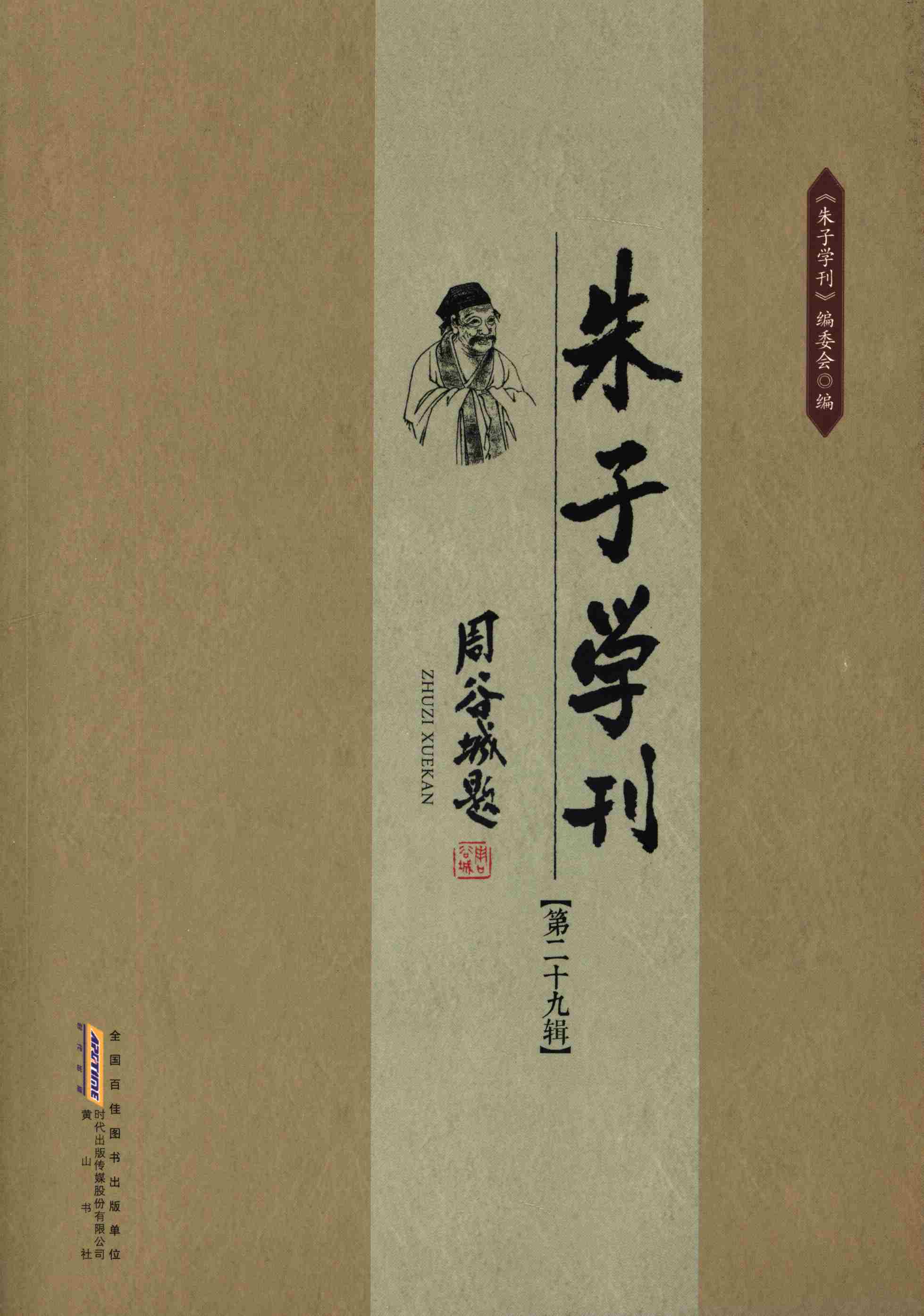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李毅婷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