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韩国朱子学的“知觉”论争——“知觉”为例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144 |
| 颗粒名称: | 第二十六章 韩国朱子学的“知觉”论争——“知觉”为例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33 |
| 页码: | 685-71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韩国朱子学中存在关于“知觉”的论争,涉及“知觉”是否属于形而上或形而下的问题。本文以“知觉”为例,探讨了韩国朱子学中的这一重要论争,并分析了牟宗三和唐君毅两位代表人物的观点。 |
| 关键词: | 韩国儒学 朱子学 知觉 |
内容
一 知觉论争的缘起与发展
17世纪朝鲜性理学的发展,不仅夹杂在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的分立中,也不免陷于政治党争的激烈对立里,其复杂性远甚于16世纪的退、栗时代。虽然如此,17世纪的朝鲜性理学者对于朱子思想,除了消化吸收外,还做了更细致与深刻的哲学省察,充分发挥朱子思想诸多命题之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其中,“知觉论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①
在栗谷学派中,掌握学术与政治发言权的性理学者,当属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0在学术上,宋时烈长于辩论,对于退溪学派多所抨击;在政治上,他属于西人的老论,历事仁、孝、显、肃四朝,每与南人激烈冲突。其门人中,尹拯(字子仁,号明斋,1629—1714)最为杰出,但因怀尼老少冲突之分裂,师、生反目成仇;故栗谷学统由另一门人权尚夏(字致道,号遂庵,又号寒水斋,1641—1721)继承。而金昌协(字仲和,号农岩,又号三洲,1651—1708)也是宋尤庵门人,不同的是,金昌协虽然属于栗谷学派,但其思想颇有异彩,并非如权尚夏般地捍卫师说。如对于“四端七情”“人心道心”等重要性理学论争,金昌协对李珥(字叔献,号栗谷,1536—1584)的说法或提出修正,或发明言外之旨。①因此,日本学者高桥亨(1878-1967)就认为金昌协是介于“主理派”与“主气派”之间的“折衷派”性理学者。②金昌协除了对退、栗时代的“四端七情”“人心道心”论争有自家看法外,对于朝鲜后期的新论争如“人物性同异论”“知觉论争”等,也提出独特的见解。而“知觉论争”就是因金昌协提出异说,主张“知觉为心之用”,才引发后期朝鲜性理学者的关切与激辩。
事实上,“知觉论争”的争议点,就在于朱子思想中,“知觉”属于“智之用”或是“心之用”。大多数的朝鲜性理学者,多认为知觉为智之用,未尝质疑。然而,在金昌协之前,其师宋时烈就发现朱子文本中,有“知觉属心之用”与“知觉属智之用”两种不一致的说法。宋时烈写于1628年的《看书杂录》就提到此问题:
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说。而一处又以知觉属智,此处不可不仔细分辨。窃谓前所谓知觉,是泛言心之虚明不昧。后所谓知觉,是《孟子》注所谓“识其事之所当然,悟其理之所以然”者。故有属心、属智之异也。③
又说:
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训说也。其《答吴晦叔》书则乃以知觉为智之用,此非前后异说也。夫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识饥饱寒暖者,心之用也,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盖心,气也;智,性也,性则理也。气与理二者不可离,而亦不可杂也。①
宋时烈一方面认为“以知觉属心”是朱子一生的训说,另一方面又在朱子诸多文本中,如《孟子集注》②《答吴晦叔》③等发现“知觉”属于“智”,或属于“智之用”的说法。不过,宋时烈并不认为朱子之说前后不一致,而是指出朱子所谓的“知觉”有两种指涉:一是心之用,如“识饥饱寒暖”;一是智之用,如“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前者指“气”言,后者就“理”说。若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说,就“心之用”而言的知觉,属于“感官知觉”(senseperception),从“智之用”来说的知觉,属于对“道德法则”(识事之所当然)与“自然法则”(悟理之所以然)的“知觉”(awareness)。问题是,这两种知觉是否有本质上的理气区分,还是两类不同的知觉而已?朱子与宋时烈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主题,进而充分讨论、提出论证的则是金昌协。
根据金昌协《年谱》的记载,金昌协于朝鲜肃宗丁丑年(1697)因反对元代胡炳文(号云峰,1250—1333)《四书通》所补充朱子论“智”的文本,与尹拯门人闵以升(字彦晖,号诚斋,1649—1697)展开辩论。金昌协于《答闵彦晖》第1书就指出争议点所在:
《大学章句序》“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小注》云峰胡氏曰:“朱子四书称仁曰心之德爱之理,义曰心之制事之宜,礼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皆兼体用。独智字,未有明释。尝欲窃取朱子之意以补之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窃谓两说,只说得心之知觉,与智字不相干涉。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确然而有准则者也。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夫以知觉,专为智之用,犹不可。况直以言智可乎?且智则理也,而谓之妙众理,谓之涵天理,则是以理妙理,以理涵理。恐尤未安也。①
虽然胡炳文的《四书通》是朝鲜性理学者理解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②,但金昌协却对胡炳文为朱子《大学章句序》“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一语所作小注提出质疑。胡炳文之小注分别以取朱子之言(“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与沈贵琁(号毅斋,生卒年不详)之说(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来界定朱子言“智”之意涵。但金昌协认为此二说是指“知觉”而言,属于心之用,并非“智之用”。换言之,“知觉”与“智”截然不同。不过,闵以升仍然遵从胡炳文之说,以“知觉”属于“智之用”。双方书信辩难六、七回③,闵以升仍然坚持己说,金昌协则“逐一辨破,发明至到”④。之后,在金昌协逝世前几年,也与李喜朝(号芝村,1655—1724)⑤、金时佐(字道以,生卒年不详)⑥等人辩论“知觉”这一论题。因此,从1697年至1707年,金昌协持续关切此论题,立论也愈加精微。
金昌协严分“知觉”与“智”,强调知觉为心之用,被当时的性理学者视为异论,因而引发进一步的论辩。金昌协逝世后,同属宋时烈门人的权尚夏得见金昌协之说,乃批驳之,与其门人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1682—1751)讨论此论题。权尚夏与韩元震的立场是一致的,均主张“知觉为智之用”,认为此说法并非意味着知觉之气为智之用,而是指智之理发于知觉上为智之用。对于权尚夏与韩元震的说法,金昌协之弟金昌翕(字子益,号三渊,1653—1722)乃著《论智字说》为亡兄辩解,而金昌协之门人鱼有凤(字舜瑞,号杞园,1672-1744)也著《知与知觉辩》,捍卫金昌协的立场。故对于朱子思想中的“智”与“知觉”之说,属于洛学的金昌协、金昌翕、鱼有凤兄弟师徒,遂与属于湖学的权尚夏、韩元震师徒之立场,针锋相对,辨析入微。其中金昌协与韩元震虽然未正式交锋,但二人的论证最为精微,值得探究。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处理知觉论争双方的论辩,只集中于金昌协“知觉”说的探讨。①
二朱子论“智”与“知觉”
如同大多数的朝鲜性理学论争一样,“知觉论争”表面上起于朱子诸多文本之间的不一致,但实际上涉及的是对于朱子思想的理解与诠释。尤其一旦涉及论争,便是以朱子思想为坐标,展开两方面的攻防,一是朱子文本的根据,一是朱子思想的逻辑性。因而,在讨论金昌协对朱子“智”与“知觉”的理解与诠释之前,有必要先梳理朱子对于“智”与觉”的相关论述。
“智”这一个概念,原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概念,而朱子对于“智”的论述,是关联着《孟子》“仁、义、礼、智”而立论的,在其中年的《仁说》与晚年的《玉山讲义》都有所阐释。而“知觉”这一个概念,则出现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它一方面是朱子论“心”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出现在朱子反对“以觉训仁”的论述中。若从朱子思想的发展来看,当今研究朱子思想的学者,大多认为朱子四十岁(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的乙丑之悟所确立的“中和新说”,奠定了其思想的义理架构,即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①此后,朱子各阶段的思想发展虽有转进,但并未离开此义理间架。之后,朱子根据“中和新说”的义理架构,与张南轩(名栻,1133—1180)往复辩论“仁”之意涵,而于四十四岁(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写下《仁说》。朱子的《仁说》,一方面阐释孟子的“四端之心”,另一方面也反驳杨龟山(名时,1053—1135)“万物与我为一”之说与谢上蔡(名良佐,1050—1103)“以觉训仁”之说。故朱子之《仁说》也论及“智”与“知觉”,并反对以“知觉”来诠释“仁”。嗣后,直到朱子晚年,朱子也对“知觉”与“智”有所论述。如朱子六十岁(淳熙己酉,1189年)所作《中庸章句序》②提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朱子六十五岁(宋光宗绍熙五年,1195年)所作《玉山讲义》也阐释“仁、义、礼、智”之义,并发挥“智藏”之说。根据上述的相关文本,笔者依循朱子思想的发展,一方面从“中和新说”、《中庸章句序》来探究朱子的“知觉”之说,另一方面从《仁说》《玉山讲义》来理解朱子对于“智”与“知觉”的诠释。③
有关朱子“中和新说”的文本,王懋竑《朱子年谱》所录的是《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1书、《答张敬夫》。①若从“中和新说”的问题意识来说,朱子思考的是工夫的入路问题。要言之,朱子苦参“中和”问题,源自于其师李延平(名侗,1093—1163)“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之训,但朱子始终无法契入。在此摸索中,朱子受到程伊川(名颐,1033—1107)“凡言心者,皆指已发”的启发,遂认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此是“中和旧说”之思路。之后,朱子又反省到“只将心性对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乃认为旧说之“已发未发命名未当”。更重要的是,朱子察觉到若以“已发之心”为工夫入手处,则未发时无涵养工夫,“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②。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必须对“心”与“性”“情”关系有重新的理解,才能找到工夫的着力点。故朱子于《答张敬夫》就开宗明义说:“因复体察得见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矣。”③接者,朱子清楚地论述其义理架构: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所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通寂感、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④
根据朱子的思路,心的存在状态有体/用、寂/感、未发/已发、静/动之区分,分别指涉“性”(中)与“情”(和)。故朱子常援引伊川修正后之言解析说:“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①虽然如此,心之自身,以其“知觉运用”又能兼体用、通寂感、含动静、贯未发已发,管摄“性”与“情”。显然地,朱子认为“心”扮演通贯“性”与“情”的中介角色,故“心统性情”最能显现“心”的定位与特性。事实上,“性”“情”视为“体”“用”关系,原是宋明理学的共识,所谓“性发为情”(性体情用),朱子也不例外。但由于朱子哲学系统中,“性”只是“理”,本身不具能动性,活动的是“气”,故体(性)不能直接下贯为用(情),必须以“心”为中介,才能使体用不相离。在这个意义下,朱子强调“心统性情”时,即意味着“心有体用”②“心之体用”③“心兼体用”④。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心”何以能扮演中介的角色?又何以能管摄“性”与“情”?此问题涉及“心”“性”“情”三者的区分与关联。就“心”之管摄“性”言,形上之“性”(理)虽具于心却不可见,必须经由形下之“心”的“知觉”(认识)作用,才能显现。另从“心”之管摄“情”言,二者虽都是气,但是“心”是“气之灵”⑤“气之精爽”⑥,具有“虚明不昧”⑦的特性,能知觉所具之“理”(性);而“情”只是“感于物”后而自然流露之“气”(动),本身不具“虚灵不昧”的知觉作用,故其动可善可恶,无法决定其方向。故“情”之中节与否,“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⑧。如此一来,就“心”与“性”言,心以其“知觉”作用来管摄“性”,故心是能知觉的认知主体。从“心”与“情”来说,情之“感物而动”的行动主体仍然在“心”(心感物而动而为情),“心”能主宰情之发用。由此可见,“心”以其“知觉”作用来管摄“性”与“情”,亦即就性而言,心可知觉性理而为认知主体;从情来看,心又可知觉外物而为行动主体。因此,牟宗三精确地诠释朱子“心统性情”之义为:“心是认知地统摄性而具有之,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之。”①换言之,道德意识与行动的成立,就在于由心之认识理而表现为中节之情(依于理,发为情)。
从上述“中和新说”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架构来看,“心”因其“知觉”作用而统摄“性”与“情”,使心循理(性)而动(情),成就道德之善的行为,并成为工夫论的枢纽。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所谓“心之知觉”,不仅能知觉感性的经验内容(如:知饥饱寒暖),也能知觉抽象的性理(如: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因此,若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不能仅以一般经验意义的“perception”来理解,而应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表象力”(Vorstellungskraft,powerofrepresentation)。②即使从前述的“感性知觉”与对“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知觉”(awareness)来说,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因“所知觉”对象的不同,而表现两种不同的知觉。此义在《中庸章句序》有更明显的表述。朱子说: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③
在此论述“道心人心”的经典性文本中,朱子明确地指出心只是一个心,以“虚灵知觉”为其特性,但因所知觉对象的不同,而有人心、道心之别。当心认知“理”时,呈现为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心;心知觉“欲”(耳目感官之欲)时,呈现为感性知觉,表现为人心。①人心与道心并非对立的概念,故道德认知与感官知觉也并不对立,两者只是知觉种类的不同,究其根源,皆属于气的活动。
就因为心之“知觉”属于气的活动,故朱子在《仁说》中,一方面阐释“仁义礼智”之性理,另一方面也驳斥“以觉训仁”。对于前者,朱子根据“中和新说”的义理架构,做更精细的排比: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人,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②
诚如李明辉所言,朱子在此列举四种不同的秩序。从天地之德来说,“元、亨、利、贞”属于存有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属于宇宙论的秩序,二者是理与气的关系。就人心之德而言,“仁、义、礼、智”属于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爱、恭、宜、别”属于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二者是性与情的关系。③对朱子而言,天地之德与人心之德相互对应,故性与情的关系,也是理与气的关系,也可以说天地之德具体化于人心之中,即是性与情的关系。就孟子四端之心的理解言,朱子认为心之所以为心,乃在于心具“仁、义、礼、智”之“性”,并以此为体,而能发用为“爱、恭、宜、别”之“情”。这样的理解,显然预设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而且朱子还在《仁说》中借“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来凸显“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以显示“仁”之独特意涵。
问题是“元统四德”与“仁包四端”(仁包四德)如何可能?依据朱子“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来细察,天地之“元”是透过宇宙论的气化过程(春生之气无所不通),而使“元”统“亨、利、贞”诸德。同样地,人心之“仁”是借由“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来包“义、礼、智”诸德。而“恻隐之心”实指“恻隐之情”,也属于“气”的作用。换言之,“元统四德”与“仁包四端”都不是从“元”“仁”作为“理”之直接统包其他三德说,而必须透过“春”“恻隐”作为“气”之活动的中介,才能间接统包其他三德。而在《元亨利贞说》中,朱子更将天地之德、人心之德都以“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架构来理解,性之能贯于情,便是以“心”为中介。①这样的思路,朱子在晚年所写的《玉山讲义》表述得更清楚:
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各自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②
又说:
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③
朱子的思维很一贯,他再度表达“仁、义、礼、智”是“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情”,性是情之表现的所以然之理,性也随具体之事而表现为情。
因而,“仁”是“温和慈爱底道理”,“智”是“分别是非底道理”,四德之性对应四端之情,各有配属,各有界限,性情体用有别。据此,“分别是非”属于“智”之事(随事发见),与“温和慈爱”之“仁”不同。“仁”与增”各只是一理,只是对应“恻隐”“是非”之情而言的一性。分解地说,“仁”与“智”不能内在地包摄其他诸德。不过,朱子也指出“仁包四端”而为全德。然依朱子“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无法从“仁”自身分析出“仁包四端”,必须借由宇宙论之气化或心性论上气的活动来关联。因而,朱子乃借由“仁字是个生底意思、”来“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由此证成“仁包四端”。朱子所谓“生底意思”是落在气化与情之相引生而彼此关联,故此“包”是气机的贯通,即由春之生而引发夏长、秋收、冬藏而彼此关联。朱子常用阴阳与春夏秋冬之气变为比喻来说明,《玉山讲义》也不例外,故“仁包四端”是以“春之生气贯彻四时”为论据来证成的。
此外,朱子于《玉山讲义》也提及“智又是义之藏”,之后在陈器之的追问下,朱子发挥“智藏”之说。朱子说: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①
虽然朱子的“智藏”之说,有其特色。②不过,“仁包四端”与“智藏四德”之说的论证是一样的,都是透过宇宙论的气化过程来证成的。在阴阳气化的循环过程中,元气为四德之长,但“贞下起元”才能成就天地之化。人心之四端犹如天地之化,“智居四端之末”,类比春夏秋冬之气化,“智”犹如“冬藏”,有终始万物之象,故“智有藏之义”。同样地,“仁为四端之首”,但类比“贞下起元”之气化循环观,智能成始成终。“仁”与“智”借由气化循环而“此理循环不穷”。依此思路推知,也可以说“智藏四德”,故朱子也说:“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义、礼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①朱子这样论述“仁包四端”“智藏四德”与“仁”“智”之终始相续,循环无间,显然不符《论语》《孟子》之义。总之,对于“仁包四端”(乃至“智藏四德”)何以可能,朱子从中年《仁说》到晚年《玉山讲义》的思维都很一致,皆是借由气化来证成。故牟宗三精准地指出:“此包此贯只是落在气与情之相引生上而见其外在地相关联而已。”②既然“仁包四端”(智藏四德)是外在地相关联,即是间接地包,必逼显心之“知觉”的中介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朱子《仁说》除阐明“仁包四德”外,也反驳谢上蔡的“以觉训仁”。朱子说:
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③
朱子并未相应地理解程明道(名颢,1032—1085)以降至上蔡所言“以觉训仁”之脉络与实义,而迳以己意理解之。朱子认为:“上蔡所谓知觉,正谓知寒暖饱饥之类尔。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也,但所用有大小尔。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为仁者为能兼之。”④严格地说,这不是上蔡之义,而是朱子对于“知觉”的理解。依朱子的理解,“知觉”作为心之认知与感觉能力而言,包含感官知觉,也包含应对酬酢、认识事理,参赞化育。心之知觉只有一个,因其认识对象与运用范围的大小而有区别,不论一般感官知觉或道德认知,基本上都是同质的,同属于“智”之用。在这个意义下,根据“仁、义、礼、智”与“爱、恭、宜、别”各有性情体用之分,朱子事实上是将“知觉”缩小,只局限在“智”之用、“智”之“事”上。故不能以仅相应于“智”之“知觉”(别是非),来理解“仁”。但从“仁包四端”亦可推至“仁包乎智”的角度说,朱子也可以认可“仁者,心有知觉”,但“知觉”不是“仁之所以得名之实”,故反对“心有知觉谓之仁”(朱子所理解的“以觉训仁”之义)。论述至此,笔者认为,就朱子“仁包四端”,驳斥“以觉训仁”脉络下的“知觉”是狭义的(偏言之)“知觉”,仅指涉“智之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朱子对于“智”与“知觉”的相关论述,必须回到“中和新说”的义理架构来思考。如是,朱子所谓的“智”乃关联着四端而界定为“分别是非底道理”,“智”是“性”,为是非之情(心)的所以然之理。但由于“智”只是理,活动是落在气上说,故必须借由“心”之知觉“分别是非底道理”,才能落实于事上显现为“分别是非”之情。在这个意义下,朱子虽然说“知觉”为“智之用”,但此“用”并非意味着“智”能真正发用,而是“智”(理)借由心之“知觉”而显现在情上,故真正发用的是“心”。由此可以判定,朱子所谓“知觉为智之用”是“虚说”,“知觉为心之用”才是“实说”,也才有真正的指涉与实义。
至于朱子“知觉”之义,因不同的言说情境与脉络,也有广义(专言之)与狭义(偏言之)之别。如在“中和新说”、《中庸章句序》的论述中,正面表述“知觉运用”“知觉不昧”“虚灵知觉”是心之所以为心的特色,此是广义的知觉,举凡感官知觉或道德认知,都涵盖其中。不过,在“仁包四端”、反对“以觉训仁”的论述中,朱子把心之知觉只局限在“智之德”,不能包含贯通其他诸德,这是狭义的知觉。尤其,此狭义的知觉论述,在反驳“以觉训仁”与忌讳佛教之“知觉运动”(作用是性)的语境下,具有负面的意义。换言之,“知觉”是气,不具有“性即理”的价值高度。①
三 金昌协论“智”与“知觉”
在前述有关朱子“智”与“知觉”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从朱子不同脉络下的文本来看,朱子的确说过“知觉”为“智之用”。但从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来看,朱子是以“知觉”作为“心”的主要功能与特色,故“知觉”是“心”之用。虽然朱子的文本是理解朱子思想的凭借,但并非必要条件,论争的精彩,就在于对朱子思想的逻辑性之掌握与阐述。因此,对金昌协而言,胡炳文、闵以升等人以知觉属于智之用,涉及的不是文义训诂的问题,而是义理的关键处,故知觉属于心之用或智之用,凸显的是“心性之辨”,这是金昌协的问题意识。在此问题意识下,金昌协一定要区分“智”与“知觉”的不同。
(一)金昌协的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金昌协与闵以升的知觉论争的导火线是胡炳文《四书通》的小注。此小注包含胡炳文之说(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与沈毅斋之说(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金昌协认为此两说所解释的正是“心之知觉”,不能以此理解“智”。在金昌协看来,此小注涉及的不仅是文义训诂上的问题,而是对朱子思想的极大误解,不能掌握朱子思想的肯綮处,故不得不辩。就文义训诂言,金昌协批评说:
云峰之训智也,虽曰辑朱子之说,而朱子说,本以释《大学》“致知”之“知”。愚未知此“知”字,果与“仁义礼智”之“智”,同乎否乎?所谓神明,所谓妙与宰者,果指性之体耶?抑指心之用耶?①
就义理而言,金昌协更指出问题所在:
云峰之训释智字,意在详备,愚非不知也。而敢有疑焉者,疑其于心性之辨未明耳。盖闻之:性者,心所具之理。心者,性所寓之器。仁、义、礼、智,所谓性也,其体至精而不可见。虚灵知觉,所谓心也,其用至妙而不可测。非性则心无所准则,非心则性不能运用,此心性之辨也。二者不能相离,而亦不容相杂。是故语心性者,即心而指性则可,认心以为性则不可。儒者之学所当精核而明辨者,莫先于此。于此或差,则堕于释氏之见矣。①
金昌协这两段论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从文义训诂来说,胡炳文取朱子之言为“智”字训解,固有其用心。但朱子《大学或问》所言“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②,本是解释“致知”之“知”。进一步参照朱子《格致补传》“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③之说法,胡炳文所引之言,的确是解释“致知”之“知”,从“心”上说,不是解释“仁、义、礼、智”之“智”,不从“性”上言。再者,“神明”一词,也出现于《孟子·尽心上》孟子的章句:“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④显然,“神明”也是就“心之用”而言,“妙”与“宰”亦然,不是用来形容“性”之体。经金昌协还原注文出处后,胡炳文之说,随之破解。故金昌协也批评胡炳文《四书通》:“失了义理真脉络。”“而类皆从文义训诂上差排推演,备礼说过,全无质悫精深自得意思。”⑤言下之意,胡炳文对朱子思想无法掌握。从金昌协对中国朱子学者的批判中,也显示出朝鲜性理学者对掌握朱子思想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在金昌协看来,胡炳文将训解“心”之注文用来训解“智”字,此乃“认心以为性”“认气为理”,已经涉及朱子思想的根本义理问题,所谓“心性之辨未明”。因为,根据朱子“中和新说”的义理间架,性是理,心与情为气。性不可见,必由心与情而显现。虽然就“心统性情”言,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但仅就心与性的关系说,二者也可以是体用关系:性为体,心为用。故金昌协说:“非性则心无所准则,非心则性不能运用。”而二者也可以是理气关系:性属于理,心属于气。此即金昌协所言:“二者不能相离,而亦不容相杂。”若聚焦于“智”与“知觉”的关系,则“仁、义、礼、智”之“智”是“性”、是“理”,而“心之神明”是就心之“虚灵知觉”言,故“知”(知觉)是“心”,属于“气”之灵。从心性论上说,心不是性,故知觉不是智;性不可见,“即心而指性”,故即知觉之心而见智之性。就理气论言,理气不杂,故知觉与智有别;但理气不离,知觉与智不离。因此,知觉论争所涉及的“知觉”究竟是“智之用”或“心之用”问题,对金昌协而言,“虽似系于训诂文义,实则究乎心性精蕴”①。换言之,金昌协有关知觉论争的问题意识就是“心性之辨”,也可以说是“理气之分合”,亦即“心性理气之辨”②,这是朱子的“义理大原头处”③。因而,从金昌协与闵以升的辩论开始,直到逝世前一年与李喜朝的辩论为止,十年之间,金昌协有关知觉论争的论述,都环绕此“心性之辨”的问题意识而展开。
(二)智与知觉的区分与关联
金昌协有关知觉的主要论说,集中于《农岩集》的《答闵彦晖》(1697)、《与李同甫》(1706)、《答道以》(1707)诸书信中。而在“心性之辨”的问题意识下,“智”与“知觉”必须严格区分,“知觉”不是“智”,也不是“智之用”。金昌协于《答闵彦晖》所提出的论据是:
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灵觉之妙而专一心之用。是非之理,故发见于灵觉之用,而要不可浑而一之也。④
《与李同甫》也分辨得更清楚:
盖知觉,专一心之德;而智则居五性之一。知觉,气之灵也;智则性之贞也。知觉属火,故光明而不昧;智属水,故渊深而含藏。知觉之功,在鉴照能运用,其妙不可测;智之功,在分别有条理,其则不可易。知觉,如蓍之德,圆而神;智,如卦之德,方而知。此其体段之偏全,气象意思之不同者。然而不可混而一之也。①
金昌协虽然在后一封书信中,提出五种对于“智”与“知觉”的区分论据,但主要的论据仍在于朱子的心性论与理气论。从心性论上说,金昌协以“智”为五性(仁义礼智信)之一,与其他四性所具之理有别。如恻隐之情所对应的就是“仁”之性,以此例推之,“智”仅是对应于“是非之心”或“分别之情”而言的所以然之理,是分别判断的标准,并不是分别是非此一活动本身。金昌协根据朱子《论语或问》“智则别之理,而其发为是非”,以及《玉山讲义》“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故有此论断。且此论断的文本与义理根据非常坚实,金昌协坚信:“朱夫子之以别训智,两见于《或问》《讲义》,皆手笔也,且其意义明的,自无可疑。”②然而,对于“知觉”的界定,就较为复杂。如前所述,根据朱子不同问题脉络,“知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的知觉,相应于“智”之“性”而仅为“智之德”,其范围局限于“智”。广义的知觉,则实指“心之虚灵知觉”,此乃心的独特功能,而与性、情有别。因此,不论恻隐(爱)、羞恶(恭)、辞让(宜)、是非(别)之情,都有“知觉”的作用。就此而言,金昌协所谓的“知觉”,当指广义的知觉,故是“专一心之用”“专一心之德”,换言之,“智”为“五性”之一,“知觉”则统称为“心之用”。一偏(智)一全(知觉),指涉不同。
另从理气论说,类比于“元亨利贞”之四德,“智”为“性之贞”,既是四性(或五性)之一,也是心中所具之“理”。而“知觉”不论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说,它是心的作用,属于“气之灵”。按照朱子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智”与“知觉”既分属心与性,同样也分属理与气,二者有别。若以知觉为“智之用”,则岂不是“认气为理”?就此而言,“智”与“知觉”的区分,即是“理气之分”。虽然如此,金昌协并未忽略朱子“理气不离”之义。金昌协说:“盖理气,本浑融无间,而理无形体,因气而著。气之运行,即物可见。故朱子尝曰:‘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言物则气与理在其中。”①金昌协很清楚就现实具体的存在言,理气不离。故“智”虽是不可见之“理”,也是形而上之体,但必须借由“虚灵之气”(心之知觉)的发用,才能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智”(理)与“知觉”(气)没有区别,反而就因为此理气、体用、心性之区分,朱子“即情而名其性”“因用而著其体”“即气而认性”之逆推式的论证成为可能。因而,金昌协强调:“是故善言性者,即气而认性而不认气为性也,因用而指体而不指用为体也。”②值得注意的是,金昌协不仅掌握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义,也掌握李栗谷“气发理乘”之说。他指出:“夫理者,一而已矣。在天而为元亨利贞,在人而为仁义礼智。……必先有理而后有气,而既有是气。则理又乘之而发见焉。即其发见者而观之,则天之四德、人之四性,固皆若因气而分,而自其本原而言之,则气前固已有此理,为四德四性之本体。而其乘气发见者,特其用耳。”③又说:“盖方其言性也,非无气也,而其本体则理也。及其言情也,非无理也,而其发用则气也。”④由这些论述看来,金昌协认为“理”在存有论上虽有其优先性,但实际发用的却是“气”;而就“理”而言的“用”,仅是“发现”之义,所谓:“理又乘之(气)而发见焉。”职是之故,当金昌协论辩“知觉”为“心之用”而非“智之用”时,可见其对朱子与李栗谷理气论的精确掌握。
固然从心性论与理气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金昌协有关“智”与“知觉”的区分,根据的是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性。但面对朱子文本不一致的问题,金昌协也有其回应。我们可以从金昌协之所以坚持知觉(知)“专一心之用”(专一心之德)来分析。金昌协当然明白主张“知觉为智之用”的说法,亦持之有故,但他却认为未必言之成理。金昌协遍考朱子书后分析说:
且如《仁说》、胡、吴、游诸书及《语类》数条之说,皆因当时学者,疑知觉之可以属仁,而言其当属乎智。至如潘书所言,又因论心性情之分,而以知觉属之心。此所谓各随地头说去者也。且不独潘书然耳,如《中庸序》论人心道心,专以知觉为言,此尤难作智之用看。当时若有人并举此两义问于先生曰:“知觉既为智之用矣,智之用何以能具此理而行此情?智之用何以为人心道心?”云尔。则先生于此,必明有判决,而其所究极同异剖析而会通之者。不但如今日之写在册子上者而已。惜乎!门人弟子无善问者,不能一言及此,而遂成千古未了之案耳。①金昌协指出朱子《仁说》《答胡广仲》②《答吴晦叔》③《答游诚之》④与《语类》⑤等文本,为驳斥湖湘学派“以觉训仁”之说,故将“知觉”只属于“智”,而有知觉为“智之事”“智之用”之说。然而,金昌协认为朱子《答潘谦之》与《中庸章句序》才是朱子论“知觉”的关键性文本。因为,《中庸章句序》言道心人心,紧扣心之知觉而言,而《答潘谦之》则论及“心性分别”。尤其,金昌协非常重视《答潘谦之》,并一度以此书为朱子的“晚年定论”⑥,此书也是金昌协的主要论据,内容如下: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则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者,心也。①
朱子言简意赅地区分心、性、情,并分别“智”与“知觉”。从义理着眼,此书显然是“中和新说”义理间架具体而微的说明。依“心统性情”来说,性与情分属理气、体用,故性为体,其内容只是理,情为用,既是“流出运用处”,则已经属于气。而性与情必须借由“心”的中介,才能使抽象之性理,落实为具体之情。所谓“心之知觉”,亦即“心有知觉”②,知觉是心的主要功能,相对于“性”与“情”,即是心以知觉“具此理”而“行此情”。更精确地说,心以其知觉作用,认知地统摄性而具有之,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之。心之知觉,既是认知的主体,也是行动的主体。因此,就“智,是非之心”的分析来说,“智”是“性”,是“所以知是非之理”;具体的行动是“情”,即“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由静态的是非之理,到动态地表现“分别是非”的行动,就是根据“心”以其知觉作用,认知是非之理而发出道德判断以主宰情而产生“是非之”(是是非非)的行为,此即是朱子“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心也”之义。由此可见,金昌协强调《答潘谦之》之重要性,义理的内在逻辑性大于文本的代表性。③
如此一来,根据朱子思想的逻辑性,若“知觉”仅局限于“智之德”而为“智之用”,则“具此理而行此情”即是“以理具理”,是“头上安头”④,不合乎逻辑,无法解读。因此,金昌协认为朱子虽有“知觉”为“智之用”与“心之用”两种说法,但二者是矛盾的。也许朱子因言说脉络而有不同的说法,所谓“各随地头说去”,但严格地从思想的逻辑性看,“知觉”为“智之用”或“心之用”是不相容的两个命题。可惜朱子弟子并未意识到此问题,否则朱子应该能有会通诸说而有所判决,不致留下此“千古未了之案”。当然,在金昌协看来,会通二者的做法,就是将“智之用”与“心之用”之“用”另加界定。故金昌协说:“盖曰心之用者,专一心之妙用而言也。曰智之用者,偏以智之端绪而言也。智之端绪,则故不能外于心。而若心之妙用,则岂可偏属于智哉?”①言下之意,不仅“智”与“知觉”有偏全之别,“智之用”与“心之用”也有偏全之分。因为知觉属“心之用”之“用”,是指“妙用”“发用”而言,“知觉”内在于心,由心直接发用,必然产生实际的行动,这是“实说”的“用”。即使“仁义礼智”四性,也要有心之“知觉”才能具体化,“知觉”并不偏属于“智之用”。若说知觉属“智之用”,则只能就“智”(性)与“分别是非”(情、心)的对应而言,是“偏以智之端绪而言”。确切地说,由是非之心之端绪,而逆推是非之理,此即是朱子常用的“即情言性”“指心认性”,具体地说,“智”之性(理)不离心之知觉而随事发现。由于“分别是非”之“知觉”(心)与“智”之性(理)是外在的关联,故知觉为“智之用”之“用”,并非意味着“智”(性理)本身能发用,而仅是意味着不可见之“智”(性理)能因心之“知觉”而发现于“情”上。故“智之用”之“用”是“随事发现”之义,亦可说“智之事”②,此“用”本身不具能动性,是“虚说”的“用”。
此外,金昌协还面对李喜朝、玄德润“知觉之何自”的提问,反驳“知觉为智之用”的说法。金昌协说:
夫使知觉而果原于智也,则德久之问而朱子之答之也,何不曰知觉是智之所发,而直以归之于气之虚灵耶?于此审之,则谓知觉为原于智,其是非得失,决矣。③
若依“智”与“知觉”的对应而言,只可以说“智”是“知觉”的所以然之理,这是从存有论的根据来说的,而“知觉”之理仅能对应于“智”。然而金昌协却在朱子《答林德久》得到回应对手的直接答案。朱子面对林德久问“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所有知觉者,自何而发端?”时,他的回答是:“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与形器渣滓正作对也。”①固然从存有论上说,知觉以智为其存在的所以然之理,但从知觉的发生论来看,“知觉”的本质构造是“气之虚灵”,它是气之发用。就此而言,知觉不原于智,当然也不属于“智之用”。
综上所述,不论从心性论或理气论上说,“智”与“知觉”必然要区分。即使言及“智之用”与“心之用”,二者之“用”,意涵也不同,一为间接的“发见”义,一为直接的“发用”(妙用)义。由此可见,金昌协对于朱子心之“知觉”的掌握,以及“知觉为心之用”的论述,实有其独特的见解。
四 金昌协论“心之知觉”
如前所述,金昌协所谓的“知觉”,是“专一心之德”,它已经从偏属于“智之德”中独立出来,指涉心的主要机能。金昌协对此有正面而精辟的分析,笔者归纳为三个要点来说明:
(一)“知觉”“虚灵”“神明”为心之特性
金昌协除辩论“知觉”为“心之用”外,更指出“知觉”是“心”的本色,他晚年所写的《答道以》就表明此义。金昌协说:
盖心有以理言者,有以知觉言者;知觉是其本色,而理则其所具也。此方细论心性情三者界分,故不但曰心,而必著知觉二字,使无混于性耳。然则此二字,正是紧要眼目,岂得为泛论者耶?且心之为心,只是一个知觉,非于知觉外别有心;而亦非于心之知觉外,别有知觉。②
金昌协更进一步以“虚灵”之气来形容“心体”(心之体段):
今试先论虚灵者之为智与否?盖此二字,于古无之,而朱夫子创造,以形容心体者。其著于《中庸序》者,犹是就此心发用处言。至于《大学》注,则专言此心具众理应万事之体用。而直以是蔽之,则其旨益可见矣。……然则心之虚灵,果何为也?盖尝思之:心者无他,气而已矣。专言则聚五行之精英,偏言则属乎火。属乎火,故能光明不昧而照烛万物。聚五行之精英,故能变化无穷,不滞于一方。心之所以虚灵,其理只如此而已。知虚灵之如此,则知觉者。亦可知矣。天下顾安有无理之气哉?而亦何必切切然强属于仁义礼智,然后方免为性外之物哉?①
金昌协认为“心”可从理、气两面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心既是“理”又是“气”,这不合乎朱子理气论的逻辑。因此,就理而言心,只能说“心具众理”,而心本身不是理。如此一来,“心”只能属于“气”,所谓:“心者无他,气而已矣。”但从心、性、情三分来看,“心”必着上“知觉”二字来形容,否则无法与“性”区分(甚至也无法与“情”区分)。言下之意,金昌协似乎认为朱子以“知觉”来界定“心”有严格的意义,不是随意的泛论。换言之,心之为心,“只是一个知觉”。“知觉”是“心”的真正指涉,一言及“心”即指“知觉”,一言及“知觉”必就“心”言。如是,“知觉”成为朱子论心的核心概念。一言以蔽之,知觉是心的本色。这样的说法,虽隐含于朱子思想中,直到金昌协的正面论述,“心之知觉”才成为一个鲜明而重要的性理学概念。
犹有进者,“心”虽属于“气”,但却是独特之气,所谓:“心者,气之精爽。”“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在这个意义下,除了可用“知觉”来指涉心外,也可以用“虚灵”来形容心的面貌与特质(心体)。金昌协甚至认为“虚灵”二字连用来形容心体,是朱子所独创。在《中庸章句序》里,朱子以“心之虚灵知觉者,一而已矣”来说明心的发用。而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则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来解释“明德”。因此,“知觉”“虚灵”二者都指涉“心”,故二者可以连言而为“虚灵知觉”。
同时,金昌协也对心之“虚灵知觉”的特性,做了更具体的描述。他认为心既然是气之灵,故它是“具五行之菁英”,故能变化无穷,妙用无方。如若要将虚灵知觉对应于“智”之德,则从五行而言,虚灵知觉偏于火,其特性是“光明不昧而照烛万理”。换言之,狭义地从“知觉”与“智”的对应而言,“知觉”的特性即是“照”。因此,金昌协在辩论中常使用镜照的比喻说:“智之于是非,固犹鉴之于妍媸。妍媸虽在物,而妍者照其为妍,媸者照其为媸,此非鉴之分别而何?智之为别,正亦如此。”①又说:“夫朱子所谓分别,正亦以知照而言,非有他也。”②在金昌协看来,“智之于是非”如鉴之于妍媸,“智”如明镜高悬,是分别是非底道理,乃不易之则;而物之妍媸,乃分别是非的结果。根据朱子“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③来说,智无运用,因而分别之作用,即在于心之知觉。故鉴之照物,分别即是“照”之作用,故金昌协以镜照喻“知”(知觉),而有“知照”一语,显示“知觉”的特性。
有趣的是,金昌协对于朱子使用“知觉”“虚灵”二字脉络的考察,也精细到锱铢必较的地步。金昌协辨析说:
但此两语,虽非有体用之分,而详味其立言命意,却自有所主。虚灵云者,状其德也(只“虚灵”二字,尽此心体用之德)。知觉云者,指其实也(心之所以为心者,只是一个知觉而已)。是亦略有不同矣。是以朱先生文字中,用此两语,各有攸当,不容差互。如《大学章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答潘谦之》书:“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是皆言心统性情之义。而一则主于解释明字,故以状其德者称之。一则主于分别心性,故以指其实者称之。此皆从分金秤上秤出来。而于前言者,可以见虚灵之兼乎用;于后言者,可以见知觉之兼乎体矣。至于《中庸序》文,专言心之所以为心,则二者并举。以先状其德而后指其实,盖取其备也。而其语意,曰虚灵而能知觉,曰虚灵底知觉云尔。非以二者为有体用之分,而必对举而言之,若云虚灵与知觉也。至其下文,只言知觉而不言虚灵,则亦以人心道心之分,只在于所知所觉、公私之异,故专以是为言。①
金昌协从朱子使用“知觉”与“虚灵”的脉络,指出此二词的立言命意各有不同的重点。“虚灵”出自《大学章句》之注“明明德”,从“虚灵”能“具众理”而言其体,就其能“应万事”而言其用,故“虚灵”是形容“此心体用之德”。至于“知觉”则在《答潘谦之》中有最明确的界定,针对心性之别,是对“心”的实际指涉。换言之,“虚灵”形容“心之德”,“知觉”指涉“心之实”。而最完备的表述则在《中庸章句序》:“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由“虚灵”“知觉”并举而非对举,可知“虚灵知觉”是“心”之特性最完备的表述。
与“知觉”“虚灵”之义相同的,还有“神明”一词。金昌协认为“心之神明”与“虚灵知觉”意涵相同。金昌协说:
《孟子·尽心》章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与此“知”字之训大略相同,此非有两个神明也。统言心,则且就人身说其为主宰。专言知,则又就心中说其为妙用。盖心是人身上神明底物事,而其所以神明,只是此个知而已。彼此参互以观,可见此二字,特以状心之妙用而非直说性也。②
金昌协指出“神明”一词出现于《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朱子章句。在此解释脉络下,“神明”可以形容心之妙用,也可以用来形容“知”。因为,一般说心,以心为一身之主宰;说“知”(虚灵知觉),则以其为心之妙用。心之所以神明,就在于“知”。因此,“神明”与“知”(虚灵知觉)可以互换而观,二者都是形容心之妙用。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昌协巧妙地将朱子所言的“知觉”“虚灵”“神明”等词有系统地关联起来,成为说明心之特性的概念。而此说明,又相应于朱子论心的内在逻辑性,将朱子隐而未发之义彰显出来,有其卓见。
(二)心之“虚灵知觉”兼体用、贯动静
虽然在朱子心性理气论中,真正的能活动主体是属于“气之灵”的“心”,但并不意味着“心”只能就动处言,只是发用。因而金昌协以“知觉”“虚灵”“神明”来形容“心”的特性时,也强调“知觉”能兼体用、贯动静,并不只偏于动处或发用时。金昌协说:
窃尝谓心之为物,本无体质方所,而又自神明不测,此“虚灵”二字之所以立,而初非有动静体用之殊者也。今也但见其体之在中者,无形可见。而不知其用之应物者,未始有迹。……况“灵”字之义,不止于静一边,尤明白易见者。今不察此,而并以为此心未发之体,此岂为识虚灵之妙者哉。至于知觉,本亦指此心全体昭昭灵灵者而为言。是虽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方寸之中,固常了然不昧。凡其耳目之聪明,身体之容仪,皆有以主宰管摄而不昏不乱者,皆是物也。今说知觉,专以此心感物而动者言之,则又岂足以尽知觉之义哉?大抵心之虚灵知觉,贯动静而兼体用。虚灵之体,即知觉之存于未发者。虚灵之用,即知觉之见于已发者,非有二也。舜瑞之说,以为虚灵无分于动静,而知觉只可言于动而不可言于静,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是盖以未发时,不容说有知觉,故须著之理二字,而却不知此时虽未有所知所觉,而若其能知能觉者,则未始不了然,何但有其理而已哉?苟有见乎此,则虚灵之不专于静,知觉之不专于动,而不当分属乎体用者,可知矣。①
金昌协针对当时学者对于“知觉”“虚灵”的误解,再度辨明。仅以玄德润(道以)为例,似乎就认为“虚灵”只能形容心之体,“知觉”则指心之用。前者属静时未发之心,后者只动时已发之心。亦即“虚灵”“知觉”分属心自身之体用、动静。不过,金昌协却反对此说法。他认为心之“虚灵”无分于动静(未发已发)、体用,“知觉”亦然。就“虚灵”言,本形容“心之德”(心之特性),因其“具众理”而言体,就其“应万事”而言用。故“虚灵”不能专属于心之静态的描述,就因为心之“虚灵”动静常存,即使人在动时之耳目聪明、身体容仪,依旧是此心之虚灵的主宰。同样地,“知觉”也不偏于心之动态的说明。即使事物未至,思虑未萌之静时,此心仍然“知觉不昧”,只是其作用隐而未显。据此,金昌协指出:未发之时,“知觉”即以“虚灵之体”的样态默存于心而不显;已发之际,“知觉”即以“虚灵之用”的发用而见诸行事。金昌协更以朱子《与吕子约论未发》①《答潘谦之》等文本来证明己说。金昌协说:“如潘书所云‘心之知觉,具此理而行此情’,亦自兼体用说。盖能具此理者,知觉之体也;能行此情者,知觉之用也。其义尤分明矣。”②如此一来,“知觉”之“具此理”言其体,“行此情”言其用;此与“虚灵”之体用义相同。在这个意义下,“虚灵”与“知觉”名异实同,兼体用而贯动静。
此外,金昌协也认为“知觉”也不能因能所之分,而质疑“知觉”之主体性与存有的常存性。金昌协说:
《中庸或问》所云“至静之时,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此虽有能所之分,而其为知觉则一而已矣。盖人心虽有知觉,而其用则因事而见。如知寒暖觉饥饱,寒暖饥饱者,所也;知觉者,能也。非所则能无所著。故知觉之用,必因此等而见。若未有寒暖饥饱之前,则虽有知觉,而亦无自以发用矣,非并与知觉之能而无之也。《或问》所谓“能知觉”“所知觉”,其分盖如此而已。何尝谓“能知觉”者非知觉,而必待有所知觉,然后乃可谓知觉也哉?③金昌协一再强调心之所以为心,就在于“知觉”。虽然在知觉的实际发用中,必然预设“能知觉”“所知觉”或“主体”“客体”的认知格局。然而,金昌协认为“知觉”必然就“能知觉”之“心”而言。尽管“能知觉”之心的发用必须见诸所知觉之对象(客体),但即使未有所知觉之对象(客体)之前,“能知觉”之作用仍然默存于心。从“知寒暖饥饱”之例可以得知,吾人并不会因未出现“寒暖饥饱”(所知觉)之现象,就否认心没有“能知觉”的能力。同样地,未发至静之时,心之知觉能具众理,虽未见诸情,但心仍未失其“能知觉”之特性。再者,根据朱子“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的能所区分,“具是非之理”的“心”与“所以是非之理”的“性”有所区别。若必须预设“能知觉”“所知觉”才能独立说“知觉”之义,无疑将“知觉”之心窄化到动时发用,反而无彰显心之“知觉”兼体用、贯动静之特性,而“知觉”为“能知觉”之主体义也将减杀。
(三)“知觉”与“情”的区分与关联
从金昌协对于“智”与“知觉”的区分中,显示朱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别”“理气”之分。但从“心统性情”的架构中,我们还可以追问“心”与“情”的区分及其关联。这一区分朱子除了零星比喻式的说明外,并未详加说明,而金昌协在论及心之知觉时,便分析“知觉”与“情”的区分与关联。金昌协说:
知觉,乃是人心全体妙用,昭昭灵灵,不昏不昧,通寂感而主性情者也。本不当专以就动处与情相比较。而今且以动一边言之,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①
又说:
鄙说“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此正是离合说。……今只请详味“非知觉则无以为情”一句,自见其宾主对待,不容混合为一。所谓“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亦曰知觉之用只于情上见之,此外更无别涂见得知觉作用处云耳,非便以情为知觉也。若于此二句分明看破,则自无疑于会动是知觉之说。盖人只为有一个觉,故事至物来,自会感动。若其如木石之无知觉,则虽事物来触而顽然不动,不动则又安有所谓情哉?然则动固是情也,而其所以能动者,非知觉而何哉?此恐无可疑者。①
这两段话以两个要点说明“知觉”与“情”的区分与关联。一是: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一是:会动底是知觉,动底是情。在朱子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架构中,性是理,心与情俱属于气。因而,心、性之别是理气之分,亦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性、情分属体、用,也是理气上下之分。然而同属于形下之气的心(知觉)与情,要如何区分呢?从动静来说,前已述及,心之“知觉”无动静之分,无论动时、静时,心都“知觉不昧”。不过,“知觉”与“情”的关联,只就“动一边”而言。一般而言,所谓“情”是指“感物而动”。但“感物而动”的主体是“心”而非“情”,亦即由于心之感物,才引发情之活动。就此而言,心之知觉为主,情为客,二者有宾主之分,故金昌协说“非知觉则无以为情”,知觉是形成情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但知觉在动时的发用,不能隐而不显,必须落实在情之动上显现,除此之外,别无作用之处,此即金昌协所言“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因此,在动的层面、气的层面上说,金昌协所谓“非知觉则无以为情”意味着知觉与情之“不杂”关系,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则显示知觉与情之“不离”关系。
显然,知觉与情这种同质的“不离不杂”,与心性、性情而言的异质之“不离不杂”关系不同,由此可进至“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的讨论。金昌协之语比照朱子所言“动处是心,动底是性”②而来,名言虽同,所指不同。朱子所谓“动处是心,动底是性”,并非意味着“心”与“性”皆能动,而是指能动的、会动的是心,而心之能动、会动的所以然之理是“性”。故“动底是性”之“动底”,不能拘泥于字面的文义理解,误以为“动的是性”,而是要从朱子思想的逻辑性来理解,指的是使“动”成为可能的是“性”,性是动之理,而非动自身。朱子比喻说:“若以谷譬之,谷便是心,那为粟、为菽、为禾、为稻底,便是性。”③从此譬喻可以得知朱子“动处是心,动底是性”之实义。不过,金昌协提出“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时,难免会让人误解,以为“动底是情”与朱子“动底是性”的意涵相同。事实上,从金昌协强调性只是理,发用的是气(心)来看,金昌协不应会误解朱子之义。故金昌协“动底是情”与朱子“动底是性”二者所指不同,不能混合为一。①金昌协“动底是情”之“动底”是就字面意义来说,即是朱子常说的“动底物事”②“动底意思”③。用现代汉语说,“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之“底”字与“的”字相通,故金昌协之语即是:“动的是情,会动的是知觉。”此义不难理解,意味着:活动的是情,会活动的是知觉。更准确地说,“知觉”是能动的主体,有活动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活动就是“情”。犹如“目”(眼)之“视觉”之于“视”(看),目之所以为目,即在于目有视的能力(视觉),此视觉能力乃成就视之活动。知觉与情之“不离不杂”由此可以索解。
金昌协上述的说法,字面上虽有些缴绕,但义理的脉络却是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知觉”与“情”之“不离不杂”的关系,与理气不同,金昌协之弟金昌翕就说:
性情之分也则其势一串,心情之判也则势有横直。然则性情之界,上下也,非经纬也。心情之际,经纬也,非上下也。性情之分,言之似易。而心情之析,勘得较难。④
金昌翕认为“心情之判”比“性情之分”更难说清楚,同时也指出“性情之分”与“心情之判”不同,性情是理气之分,故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超越区分。但“心情之判”不是理气之别,二者同属于气而彼此交错,故以“经纬”关系喻之。事实上,朝鲜性理学中首先使用“经纬说”来理解朱子思想的是被归属于退溪学派的张显光(字德晦,号旅轩,1554—1637)。他在《性理说》中阐发“理气经纬说”。其实,“经纬”是一种譬喻,根据张显光的解释:“经即织缕之纵而在柚者也,纬即织丝之横而在杼者也。经则自始至终,通贯直达而无有变易;纬则一左一右,反复往来,而须备曲折。”①据此,他在论“在人经纬”时,也提出了“性情经纬”说。金昌协曾运用此譬喻,也指出:“盖性为经,而情为纬,错综迭为体用。须如此看,方为活络,且似周尽。”②情之为用,变化万端;性之为体,其理恒定。二者交迭,不离不杂。而金昌翕也将金昌协的心情关系以“经纬”喻之,亦即“知觉”为经,“情”为纬,因为在情的多样变化中,皆是一心之“知觉”的发用。这样的譬喻,金昌协虽未用于“知觉”与“情”的分析,但从其思想的逻辑性来看,应能接受其弟的诠释,此种诠释也呈现朝鲜性理学独有的特色。
五 结语
朝鲜后期性理学的“知觉论争”,由宋时烈启其端,继而由金昌协正式将此论题主题化(thematize),提出“知觉”为“心之用”的论据,由此引发朝鲜性理学者的关注,直至韩元震仍以“知觉”是“智之用”与之激辩。在金昌协之前的朝鲜性理学者,并未对朱子思想中“智”与“知觉”所隐含的哲学问题加以思考,而金昌协将此论题提至哲学高度来探究,有其卓见。金昌协认为不论从朱子心性论或理气论来深究,“智”为性、为理,“知觉”为心、为气的区分不容含混。换言之,“智”与“知觉”之辨,即是心性理气之辨。在此问题意识下,金昌协指出朱子言“智”只限于五性(仁义礼智性)之一,但朱子言“知觉”则专属“一心之德”,“知觉”并非只是与“智”对应配属的“智之德”而已,而是心之所以为心的本色与特性。金昌协也能掌握朱子“性只是理”与李栗谷“气发理乘一途说”之义,在区分“智”与“知觉”之际,指出真正能发用的是气,是知觉,故“知觉”不是“智之用”而是“心之用”。
更重要的是,在论证上,金昌协以朱子《答潘谦之》为文本根据,“中和新说”之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为义理间架,证成心之“知觉”能“具此理”而“行此情”,统摄性与情而成为朱子论心的重要概念。金昌协不仅以“知觉”来界定“心”的特性,还认为“虚灵”“神明”亦能形容心之特性。在金昌协看来,“虚灵知觉”最能彰显心之特性,它兼体用而贯动静。犹有进者,金昌协还进一步辨析“知觉”与“情”的关系,从动时、气的层面指出:“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其弟金昌翕还以“经纬”的交错迭用,解释心(知觉)与情的不离不杂。此种辨析与思路,并未见于中国朱子学的思维架构,但却早已出现在朝鲜性理学“四端七情”的论述中,颇具朝鲜性理学的特色。
不过如同“四端七情”所引发的“道德情感”(四端)与“一般情感”(七情)的异同,从哲学反思来说,金昌协以“知觉”为“心”的主要作用,则心之“知觉”,是否有对“道德法则”“自然法则”与“感官”的异质区分?朱子与金昌协似乎未意识到此问题。在这个意义下,“知觉”是属于“智之用”或“心之用”,也涉及“理发”或“气发”的根本问题,或是道德意识的成立问题。这样的提问,以不同的讨论类型,出现在朱子学、阳明学与朝鲜性理学的论述中,甚至涉及儒、释之辨。①且从东亚儒学的视域来看,相较于朝鲜后期的“人物性同异论”论争,“知觉”论争反而是一跨文化的哲学论题,亟待深究。
17世纪朝鲜性理学的发展,不仅夹杂在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的分立中,也不免陷于政治党争的激烈对立里,其复杂性远甚于16世纪的退、栗时代。虽然如此,17世纪的朝鲜性理学者对于朱子思想,除了消化吸收外,还做了更细致与深刻的哲学省察,充分发挥朱子思想诸多命题之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其中,“知觉论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①
在栗谷学派中,掌握学术与政治发言权的性理学者,当属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0在学术上,宋时烈长于辩论,对于退溪学派多所抨击;在政治上,他属于西人的老论,历事仁、孝、显、肃四朝,每与南人激烈冲突。其门人中,尹拯(字子仁,号明斋,1629—1714)最为杰出,但因怀尼老少冲突之分裂,师、生反目成仇;故栗谷学统由另一门人权尚夏(字致道,号遂庵,又号寒水斋,1641—1721)继承。而金昌协(字仲和,号农岩,又号三洲,1651—1708)也是宋尤庵门人,不同的是,金昌协虽然属于栗谷学派,但其思想颇有异彩,并非如权尚夏般地捍卫师说。如对于“四端七情”“人心道心”等重要性理学论争,金昌协对李珥(字叔献,号栗谷,1536—1584)的说法或提出修正,或发明言外之旨。①因此,日本学者高桥亨(1878-1967)就认为金昌协是介于“主理派”与“主气派”之间的“折衷派”性理学者。②金昌协除了对退、栗时代的“四端七情”“人心道心”论争有自家看法外,对于朝鲜后期的新论争如“人物性同异论”“知觉论争”等,也提出独特的见解。而“知觉论争”就是因金昌协提出异说,主张“知觉为心之用”,才引发后期朝鲜性理学者的关切与激辩。
事实上,“知觉论争”的争议点,就在于朱子思想中,“知觉”属于“智之用”或是“心之用”。大多数的朝鲜性理学者,多认为知觉为智之用,未尝质疑。然而,在金昌协之前,其师宋时烈就发现朱子文本中,有“知觉属心之用”与“知觉属智之用”两种不一致的说法。宋时烈写于1628年的《看书杂录》就提到此问题:
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说。而一处又以知觉属智,此处不可不仔细分辨。窃谓前所谓知觉,是泛言心之虚明不昧。后所谓知觉,是《孟子》注所谓“识其事之所当然,悟其理之所以然”者。故有属心、属智之异也。③
又说:
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训说也。其《答吴晦叔》书则乃以知觉为智之用,此非前后异说也。夫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识饥饱寒暖者,心之用也,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盖心,气也;智,性也,性则理也。气与理二者不可离,而亦不可杂也。①
宋时烈一方面认为“以知觉属心”是朱子一生的训说,另一方面又在朱子诸多文本中,如《孟子集注》②《答吴晦叔》③等发现“知觉”属于“智”,或属于“智之用”的说法。不过,宋时烈并不认为朱子之说前后不一致,而是指出朱子所谓的“知觉”有两种指涉:一是心之用,如“识饥饱寒暖”;一是智之用,如“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前者指“气”言,后者就“理”说。若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说,就“心之用”而言的知觉,属于“感官知觉”(senseperception),从“智之用”来说的知觉,属于对“道德法则”(识事之所当然)与“自然法则”(悟理之所以然)的“知觉”(awareness)。问题是,这两种知觉是否有本质上的理气区分,还是两类不同的知觉而已?朱子与宋时烈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主题,进而充分讨论、提出论证的则是金昌协。
根据金昌协《年谱》的记载,金昌协于朝鲜肃宗丁丑年(1697)因反对元代胡炳文(号云峰,1250—1333)《四书通》所补充朱子论“智”的文本,与尹拯门人闵以升(字彦晖,号诚斋,1649—1697)展开辩论。金昌协于《答闵彦晖》第1书就指出争议点所在:
《大学章句序》“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小注》云峰胡氏曰:“朱子四书称仁曰心之德爱之理,义曰心之制事之宜,礼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皆兼体用。独智字,未有明释。尝欲窃取朱子之意以补之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窃谓两说,只说得心之知觉,与智字不相干涉。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确然而有准则者也。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夫以知觉,专为智之用,犹不可。况直以言智可乎?且智则理也,而谓之妙众理,谓之涵天理,则是以理妙理,以理涵理。恐尤未安也。①
虽然胡炳文的《四书通》是朝鲜性理学者理解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②,但金昌协却对胡炳文为朱子《大学章句序》“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一语所作小注提出质疑。胡炳文之小注分别以取朱子之言(“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与沈贵琁(号毅斋,生卒年不详)之说(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来界定朱子言“智”之意涵。但金昌协认为此二说是指“知觉”而言,属于心之用,并非“智之用”。换言之,“知觉”与“智”截然不同。不过,闵以升仍然遵从胡炳文之说,以“知觉”属于“智之用”。双方书信辩难六、七回③,闵以升仍然坚持己说,金昌协则“逐一辨破,发明至到”④。之后,在金昌协逝世前几年,也与李喜朝(号芝村,1655—1724)⑤、金时佐(字道以,生卒年不详)⑥等人辩论“知觉”这一论题。因此,从1697年至1707年,金昌协持续关切此论题,立论也愈加精微。
金昌协严分“知觉”与“智”,强调知觉为心之用,被当时的性理学者视为异论,因而引发进一步的论辩。金昌协逝世后,同属宋时烈门人的权尚夏得见金昌协之说,乃批驳之,与其门人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1682—1751)讨论此论题。权尚夏与韩元震的立场是一致的,均主张“知觉为智之用”,认为此说法并非意味着知觉之气为智之用,而是指智之理发于知觉上为智之用。对于权尚夏与韩元震的说法,金昌协之弟金昌翕(字子益,号三渊,1653—1722)乃著《论智字说》为亡兄辩解,而金昌协之门人鱼有凤(字舜瑞,号杞园,1672-1744)也著《知与知觉辩》,捍卫金昌协的立场。故对于朱子思想中的“智”与“知觉”之说,属于洛学的金昌协、金昌翕、鱼有凤兄弟师徒,遂与属于湖学的权尚夏、韩元震师徒之立场,针锋相对,辨析入微。其中金昌协与韩元震虽然未正式交锋,但二人的论证最为精微,值得探究。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处理知觉论争双方的论辩,只集中于金昌协“知觉”说的探讨。①
二朱子论“智”与“知觉”
如同大多数的朝鲜性理学论争一样,“知觉论争”表面上起于朱子诸多文本之间的不一致,但实际上涉及的是对于朱子思想的理解与诠释。尤其一旦涉及论争,便是以朱子思想为坐标,展开两方面的攻防,一是朱子文本的根据,一是朱子思想的逻辑性。因而,在讨论金昌协对朱子“智”与“知觉”的理解与诠释之前,有必要先梳理朱子对于“智”与觉”的相关论述。
“智”这一个概念,原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概念,而朱子对于“智”的论述,是关联着《孟子》“仁、义、礼、智”而立论的,在其中年的《仁说》与晚年的《玉山讲义》都有所阐释。而“知觉”这一个概念,则出现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它一方面是朱子论“心”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出现在朱子反对“以觉训仁”的论述中。若从朱子思想的发展来看,当今研究朱子思想的学者,大多认为朱子四十岁(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的乙丑之悟所确立的“中和新说”,奠定了其思想的义理架构,即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①此后,朱子各阶段的思想发展虽有转进,但并未离开此义理间架。之后,朱子根据“中和新说”的义理架构,与张南轩(名栻,1133—1180)往复辩论“仁”之意涵,而于四十四岁(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写下《仁说》。朱子的《仁说》,一方面阐释孟子的“四端之心”,另一方面也反驳杨龟山(名时,1053—1135)“万物与我为一”之说与谢上蔡(名良佐,1050—1103)“以觉训仁”之说。故朱子之《仁说》也论及“智”与“知觉”,并反对以“知觉”来诠释“仁”。嗣后,直到朱子晚年,朱子也对“知觉”与“智”有所论述。如朱子六十岁(淳熙己酉,1189年)所作《中庸章句序》②提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朱子六十五岁(宋光宗绍熙五年,1195年)所作《玉山讲义》也阐释“仁、义、礼、智”之义,并发挥“智藏”之说。根据上述的相关文本,笔者依循朱子思想的发展,一方面从“中和新说”、《中庸章句序》来探究朱子的“知觉”之说,另一方面从《仁说》《玉山讲义》来理解朱子对于“智”与“知觉”的诠释。③
有关朱子“中和新说”的文本,王懋竑《朱子年谱》所录的是《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1书、《答张敬夫》。①若从“中和新说”的问题意识来说,朱子思考的是工夫的入路问题。要言之,朱子苦参“中和”问题,源自于其师李延平(名侗,1093—1163)“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之训,但朱子始终无法契入。在此摸索中,朱子受到程伊川(名颐,1033—1107)“凡言心者,皆指已发”的启发,遂认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此是“中和旧说”之思路。之后,朱子又反省到“只将心性对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乃认为旧说之“已发未发命名未当”。更重要的是,朱子察觉到若以“已发之心”为工夫入手处,则未发时无涵养工夫,“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②。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必须对“心”与“性”“情”关系有重新的理解,才能找到工夫的着力点。故朱子于《答张敬夫》就开宗明义说:“因复体察得见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矣。”③接者,朱子清楚地论述其义理架构: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所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通寂感、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④
根据朱子的思路,心的存在状态有体/用、寂/感、未发/已发、静/动之区分,分别指涉“性”(中)与“情”(和)。故朱子常援引伊川修正后之言解析说:“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①虽然如此,心之自身,以其“知觉运用”又能兼体用、通寂感、含动静、贯未发已发,管摄“性”与“情”。显然地,朱子认为“心”扮演通贯“性”与“情”的中介角色,故“心统性情”最能显现“心”的定位与特性。事实上,“性”“情”视为“体”“用”关系,原是宋明理学的共识,所谓“性发为情”(性体情用),朱子也不例外。但由于朱子哲学系统中,“性”只是“理”,本身不具能动性,活动的是“气”,故体(性)不能直接下贯为用(情),必须以“心”为中介,才能使体用不相离。在这个意义下,朱子强调“心统性情”时,即意味着“心有体用”②“心之体用”③“心兼体用”④。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心”何以能扮演中介的角色?又何以能管摄“性”与“情”?此问题涉及“心”“性”“情”三者的区分与关联。就“心”之管摄“性”言,形上之“性”(理)虽具于心却不可见,必须经由形下之“心”的“知觉”(认识)作用,才能显现。另从“心”之管摄“情”言,二者虽都是气,但是“心”是“气之灵”⑤“气之精爽”⑥,具有“虚明不昧”⑦的特性,能知觉所具之“理”(性);而“情”只是“感于物”后而自然流露之“气”(动),本身不具“虚灵不昧”的知觉作用,故其动可善可恶,无法决定其方向。故“情”之中节与否,“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⑧。如此一来,就“心”与“性”言,心以其“知觉”作用来管摄“性”,故心是能知觉的认知主体。从“心”与“情”来说,情之“感物而动”的行动主体仍然在“心”(心感物而动而为情),“心”能主宰情之发用。由此可见,“心”以其“知觉”作用来管摄“性”与“情”,亦即就性而言,心可知觉性理而为认知主体;从情来看,心又可知觉外物而为行动主体。因此,牟宗三精确地诠释朱子“心统性情”之义为:“心是认知地统摄性而具有之,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之。”①换言之,道德意识与行动的成立,就在于由心之认识理而表现为中节之情(依于理,发为情)。
从上述“中和新说”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架构来看,“心”因其“知觉”作用而统摄“性”与“情”,使心循理(性)而动(情),成就道德之善的行为,并成为工夫论的枢纽。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所谓“心之知觉”,不仅能知觉感性的经验内容(如:知饥饱寒暖),也能知觉抽象的性理(如: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因此,若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不能仅以一般经验意义的“perception”来理解,而应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表象力”(Vorstellungskraft,powerofrepresentation)。②即使从前述的“感性知觉”与对“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知觉”(awareness)来说,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因“所知觉”对象的不同,而表现两种不同的知觉。此义在《中庸章句序》有更明显的表述。朱子说: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③
在此论述“道心人心”的经典性文本中,朱子明确地指出心只是一个心,以“虚灵知觉”为其特性,但因所知觉对象的不同,而有人心、道心之别。当心认知“理”时,呈现为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心;心知觉“欲”(耳目感官之欲)时,呈现为感性知觉,表现为人心。①人心与道心并非对立的概念,故道德认知与感官知觉也并不对立,两者只是知觉种类的不同,究其根源,皆属于气的活动。
就因为心之“知觉”属于气的活动,故朱子在《仁说》中,一方面阐释“仁义礼智”之性理,另一方面也驳斥“以觉训仁”。对于前者,朱子根据“中和新说”的义理架构,做更精细的排比: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人,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②
诚如李明辉所言,朱子在此列举四种不同的秩序。从天地之德来说,“元、亨、利、贞”属于存有论的秩序;“春、夏、秋、冬”属于宇宙论的秩序,二者是理与气的关系。就人心之德而言,“仁、义、礼、智”属于存有—伦理学的(onto-ethical)秩序;“爱、恭、宜、别”属于伦理—心理学的(ethico-psychological)秩序,二者是性与情的关系。③对朱子而言,天地之德与人心之德相互对应,故性与情的关系,也是理与气的关系,也可以说天地之德具体化于人心之中,即是性与情的关系。就孟子四端之心的理解言,朱子认为心之所以为心,乃在于心具“仁、义、礼、智”之“性”,并以此为体,而能发用为“爱、恭、宜、别”之“情”。这样的理解,显然预设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而且朱子还在《仁说》中借“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来凸显“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以显示“仁”之独特意涵。
问题是“元统四德”与“仁包四端”(仁包四德)如何可能?依据朱子“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来细察,天地之“元”是透过宇宙论的气化过程(春生之气无所不通),而使“元”统“亨、利、贞”诸德。同样地,人心之“仁”是借由“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来包“义、礼、智”诸德。而“恻隐之心”实指“恻隐之情”,也属于“气”的作用。换言之,“元统四德”与“仁包四端”都不是从“元”“仁”作为“理”之直接统包其他三德说,而必须透过“春”“恻隐”作为“气”之活动的中介,才能间接统包其他三德。而在《元亨利贞说》中,朱子更将天地之德、人心之德都以“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架构来理解,性之能贯于情,便是以“心”为中介。①这样的思路,朱子在晚年所写的《玉山讲义》表述得更清楚:
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各自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②
又说:
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③
朱子的思维很一贯,他再度表达“仁、义、礼、智”是“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情”,性是情之表现的所以然之理,性也随具体之事而表现为情。
因而,“仁”是“温和慈爱底道理”,“智”是“分别是非底道理”,四德之性对应四端之情,各有配属,各有界限,性情体用有别。据此,“分别是非”属于“智”之事(随事发见),与“温和慈爱”之“仁”不同。“仁”与增”各只是一理,只是对应“恻隐”“是非”之情而言的一性。分解地说,“仁”与“智”不能内在地包摄其他诸德。不过,朱子也指出“仁包四端”而为全德。然依朱子“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无法从“仁”自身分析出“仁包四端”,必须借由宇宙论之气化或心性论上气的活动来关联。因而,朱子乃借由“仁字是个生底意思、”来“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由此证成“仁包四端”。朱子所谓“生底意思”是落在气化与情之相引生而彼此关联,故此“包”是气机的贯通,即由春之生而引发夏长、秋收、冬藏而彼此关联。朱子常用阴阳与春夏秋冬之气变为比喻来说明,《玉山讲义》也不例外,故“仁包四端”是以“春之生气贯彻四时”为论据来证成的。
此外,朱子于《玉山讲义》也提及“智又是义之藏”,之后在陈器之的追问下,朱子发挥“智藏”之说。朱子说: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①
虽然朱子的“智藏”之说,有其特色。②不过,“仁包四端”与“智藏四德”之说的论证是一样的,都是透过宇宙论的气化过程来证成的。在阴阳气化的循环过程中,元气为四德之长,但“贞下起元”才能成就天地之化。人心之四端犹如天地之化,“智居四端之末”,类比春夏秋冬之气化,“智”犹如“冬藏”,有终始万物之象,故“智有藏之义”。同样地,“仁为四端之首”,但类比“贞下起元”之气化循环观,智能成始成终。“仁”与“智”借由气化循环而“此理循环不穷”。依此思路推知,也可以说“智藏四德”,故朱子也说:“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义、礼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①朱子这样论述“仁包四端”“智藏四德”与“仁”“智”之终始相续,循环无间,显然不符《论语》《孟子》之义。总之,对于“仁包四端”(乃至“智藏四德”)何以可能,朱子从中年《仁说》到晚年《玉山讲义》的思维都很一致,皆是借由气化来证成。故牟宗三精准地指出:“此包此贯只是落在气与情之相引生上而见其外在地相关联而已。”②既然“仁包四端”(智藏四德)是外在地相关联,即是间接地包,必逼显心之“知觉”的中介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朱子《仁说》除阐明“仁包四德”外,也反驳谢上蔡的“以觉训仁”。朱子说:
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③
朱子并未相应地理解程明道(名颢,1032—1085)以降至上蔡所言“以觉训仁”之脉络与实义,而迳以己意理解之。朱子认为:“上蔡所谓知觉,正谓知寒暖饱饥之类尔。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也,但所用有大小尔。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为仁者为能兼之。”④严格地说,这不是上蔡之义,而是朱子对于“知觉”的理解。依朱子的理解,“知觉”作为心之认知与感觉能力而言,包含感官知觉,也包含应对酬酢、认识事理,参赞化育。心之知觉只有一个,因其认识对象与运用范围的大小而有区别,不论一般感官知觉或道德认知,基本上都是同质的,同属于“智”之用。在这个意义下,根据“仁、义、礼、智”与“爱、恭、宜、别”各有性情体用之分,朱子事实上是将“知觉”缩小,只局限在“智”之用、“智”之“事”上。故不能以仅相应于“智”之“知觉”(别是非),来理解“仁”。但从“仁包四端”亦可推至“仁包乎智”的角度说,朱子也可以认可“仁者,心有知觉”,但“知觉”不是“仁之所以得名之实”,故反对“心有知觉谓之仁”(朱子所理解的“以觉训仁”之义)。论述至此,笔者认为,就朱子“仁包四端”,驳斥“以觉训仁”脉络下的“知觉”是狭义的(偏言之)“知觉”,仅指涉“智之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朱子对于“智”与“知觉”的相关论述,必须回到“中和新说”的义理架构来思考。如是,朱子所谓的“智”乃关联着四端而界定为“分别是非底道理”,“智”是“性”,为是非之情(心)的所以然之理。但由于“智”只是理,活动是落在气上说,故必须借由“心”之知觉“分别是非底道理”,才能落实于事上显现为“分别是非”之情。在这个意义下,朱子虽然说“知觉”为“智之用”,但此“用”并非意味着“智”能真正发用,而是“智”(理)借由心之“知觉”而显现在情上,故真正发用的是“心”。由此可以判定,朱子所谓“知觉为智之用”是“虚说”,“知觉为心之用”才是“实说”,也才有真正的指涉与实义。
至于朱子“知觉”之义,因不同的言说情境与脉络,也有广义(专言之)与狭义(偏言之)之别。如在“中和新说”、《中庸章句序》的论述中,正面表述“知觉运用”“知觉不昧”“虚灵知觉”是心之所以为心的特色,此是广义的知觉,举凡感官知觉或道德认知,都涵盖其中。不过,在“仁包四端”、反对“以觉训仁”的论述中,朱子把心之知觉只局限在“智之德”,不能包含贯通其他诸德,这是狭义的知觉。尤其,此狭义的知觉论述,在反驳“以觉训仁”与忌讳佛教之“知觉运动”(作用是性)的语境下,具有负面的意义。换言之,“知觉”是气,不具有“性即理”的价值高度。①
三 金昌协论“智”与“知觉”
在前述有关朱子“智”与“知觉”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从朱子不同脉络下的文本来看,朱子的确说过“知觉”为“智之用”。但从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来看,朱子是以“知觉”作为“心”的主要功能与特色,故“知觉”是“心”之用。虽然朱子的文本是理解朱子思想的凭借,但并非必要条件,论争的精彩,就在于对朱子思想的逻辑性之掌握与阐述。因此,对金昌协而言,胡炳文、闵以升等人以知觉属于智之用,涉及的不是文义训诂的问题,而是义理的关键处,故知觉属于心之用或智之用,凸显的是“心性之辨”,这是金昌协的问题意识。在此问题意识下,金昌协一定要区分“智”与“知觉”的不同。
(一)金昌协的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金昌协与闵以升的知觉论争的导火线是胡炳文《四书通》的小注。此小注包含胡炳文之说(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与沈毅斋之说(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金昌协认为此两说所解释的正是“心之知觉”,不能以此理解“智”。在金昌协看来,此小注涉及的不仅是文义训诂上的问题,而是对朱子思想的极大误解,不能掌握朱子思想的肯綮处,故不得不辩。就文义训诂言,金昌协批评说:
云峰之训智也,虽曰辑朱子之说,而朱子说,本以释《大学》“致知”之“知”。愚未知此“知”字,果与“仁义礼智”之“智”,同乎否乎?所谓神明,所谓妙与宰者,果指性之体耶?抑指心之用耶?①
就义理而言,金昌协更指出问题所在:
云峰之训释智字,意在详备,愚非不知也。而敢有疑焉者,疑其于心性之辨未明耳。盖闻之:性者,心所具之理。心者,性所寓之器。仁、义、礼、智,所谓性也,其体至精而不可见。虚灵知觉,所谓心也,其用至妙而不可测。非性则心无所准则,非心则性不能运用,此心性之辨也。二者不能相离,而亦不容相杂。是故语心性者,即心而指性则可,认心以为性则不可。儒者之学所当精核而明辨者,莫先于此。于此或差,则堕于释氏之见矣。①
金昌协这两段论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从文义训诂来说,胡炳文取朱子之言为“智”字训解,固有其用心。但朱子《大学或问》所言“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②,本是解释“致知”之“知”。进一步参照朱子《格致补传》“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③之说法,胡炳文所引之言,的确是解释“致知”之“知”,从“心”上说,不是解释“仁、义、礼、智”之“智”,不从“性”上言。再者,“神明”一词,也出现于《孟子·尽心上》孟子的章句:“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④显然,“神明”也是就“心之用”而言,“妙”与“宰”亦然,不是用来形容“性”之体。经金昌协还原注文出处后,胡炳文之说,随之破解。故金昌协也批评胡炳文《四书通》:“失了义理真脉络。”“而类皆从文义训诂上差排推演,备礼说过,全无质悫精深自得意思。”⑤言下之意,胡炳文对朱子思想无法掌握。从金昌协对中国朱子学者的批判中,也显示出朝鲜性理学者对掌握朱子思想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在金昌协看来,胡炳文将训解“心”之注文用来训解“智”字,此乃“认心以为性”“认气为理”,已经涉及朱子思想的根本义理问题,所谓“心性之辨未明”。因为,根据朱子“中和新说”的义理间架,性是理,心与情为气。性不可见,必由心与情而显现。虽然就“心统性情”言,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但仅就心与性的关系说,二者也可以是体用关系:性为体,心为用。故金昌协说:“非性则心无所准则,非心则性不能运用。”而二者也可以是理气关系:性属于理,心属于气。此即金昌协所言:“二者不能相离,而亦不容相杂。”若聚焦于“智”与“知觉”的关系,则“仁、义、礼、智”之“智”是“性”、是“理”,而“心之神明”是就心之“虚灵知觉”言,故“知”(知觉)是“心”,属于“气”之灵。从心性论上说,心不是性,故知觉不是智;性不可见,“即心而指性”,故即知觉之心而见智之性。就理气论言,理气不杂,故知觉与智有别;但理气不离,知觉与智不离。因此,知觉论争所涉及的“知觉”究竟是“智之用”或“心之用”问题,对金昌协而言,“虽似系于训诂文义,实则究乎心性精蕴”①。换言之,金昌协有关知觉论争的问题意识就是“心性之辨”,也可以说是“理气之分合”,亦即“心性理气之辨”②,这是朱子的“义理大原头处”③。因而,从金昌协与闵以升的辩论开始,直到逝世前一年与李喜朝的辩论为止,十年之间,金昌协有关知觉论争的论述,都环绕此“心性之辨”的问题意识而展开。
(二)智与知觉的区分与关联
金昌协有关知觉的主要论说,集中于《农岩集》的《答闵彦晖》(1697)、《与李同甫》(1706)、《答道以》(1707)诸书信中。而在“心性之辨”的问题意识下,“智”与“知觉”必须严格区分,“知觉”不是“智”,也不是“智之用”。金昌协于《答闵彦晖》所提出的论据是:
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灵觉之妙而专一心之用。是非之理,故发见于灵觉之用,而要不可浑而一之也。④
《与李同甫》也分辨得更清楚:
盖知觉,专一心之德;而智则居五性之一。知觉,气之灵也;智则性之贞也。知觉属火,故光明而不昧;智属水,故渊深而含藏。知觉之功,在鉴照能运用,其妙不可测;智之功,在分别有条理,其则不可易。知觉,如蓍之德,圆而神;智,如卦之德,方而知。此其体段之偏全,气象意思之不同者。然而不可混而一之也。①
金昌协虽然在后一封书信中,提出五种对于“智”与“知觉”的区分论据,但主要的论据仍在于朱子的心性论与理气论。从心性论上说,金昌协以“智”为五性(仁义礼智信)之一,与其他四性所具之理有别。如恻隐之情所对应的就是“仁”之性,以此例推之,“智”仅是对应于“是非之心”或“分别之情”而言的所以然之理,是分别判断的标准,并不是分别是非此一活动本身。金昌协根据朱子《论语或问》“智则别之理,而其发为是非”,以及《玉山讲义》“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故有此论断。且此论断的文本与义理根据非常坚实,金昌协坚信:“朱夫子之以别训智,两见于《或问》《讲义》,皆手笔也,且其意义明的,自无可疑。”②然而,对于“知觉”的界定,就较为复杂。如前所述,根据朱子不同问题脉络,“知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的知觉,相应于“智”之“性”而仅为“智之德”,其范围局限于“智”。广义的知觉,则实指“心之虚灵知觉”,此乃心的独特功能,而与性、情有别。因此,不论恻隐(爱)、羞恶(恭)、辞让(宜)、是非(别)之情,都有“知觉”的作用。就此而言,金昌协所谓的“知觉”,当指广义的知觉,故是“专一心之用”“专一心之德”,换言之,“智”为“五性”之一,“知觉”则统称为“心之用”。一偏(智)一全(知觉),指涉不同。
另从理气论说,类比于“元亨利贞”之四德,“智”为“性之贞”,既是四性(或五性)之一,也是心中所具之“理”。而“知觉”不论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说,它是心的作用,属于“气之灵”。按照朱子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智”与“知觉”既分属心与性,同样也分属理与气,二者有别。若以知觉为“智之用”,则岂不是“认气为理”?就此而言,“智”与“知觉”的区分,即是“理气之分”。虽然如此,金昌协并未忽略朱子“理气不离”之义。金昌协说:“盖理气,本浑融无间,而理无形体,因气而著。气之运行,即物可见。故朱子尝曰:‘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言物则气与理在其中。”①金昌协很清楚就现实具体的存在言,理气不离。故“智”虽是不可见之“理”,也是形而上之体,但必须借由“虚灵之气”(心之知觉)的发用,才能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智”(理)与“知觉”(气)没有区别,反而就因为此理气、体用、心性之区分,朱子“即情而名其性”“因用而著其体”“即气而认性”之逆推式的论证成为可能。因而,金昌协强调:“是故善言性者,即气而认性而不认气为性也,因用而指体而不指用为体也。”②值得注意的是,金昌协不仅掌握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义,也掌握李栗谷“气发理乘”之说。他指出:“夫理者,一而已矣。在天而为元亨利贞,在人而为仁义礼智。……必先有理而后有气,而既有是气。则理又乘之而发见焉。即其发见者而观之,则天之四德、人之四性,固皆若因气而分,而自其本原而言之,则气前固已有此理,为四德四性之本体。而其乘气发见者,特其用耳。”③又说:“盖方其言性也,非无气也,而其本体则理也。及其言情也,非无理也,而其发用则气也。”④由这些论述看来,金昌协认为“理”在存有论上虽有其优先性,但实际发用的却是“气”;而就“理”而言的“用”,仅是“发现”之义,所谓:“理又乘之(气)而发见焉。”职是之故,当金昌协论辩“知觉”为“心之用”而非“智之用”时,可见其对朱子与李栗谷理气论的精确掌握。
固然从心性论与理气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金昌协有关“智”与“知觉”的区分,根据的是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性。但面对朱子文本不一致的问题,金昌协也有其回应。我们可以从金昌协之所以坚持知觉(知)“专一心之用”(专一心之德)来分析。金昌协当然明白主张“知觉为智之用”的说法,亦持之有故,但他却认为未必言之成理。金昌协遍考朱子书后分析说:
且如《仁说》、胡、吴、游诸书及《语类》数条之说,皆因当时学者,疑知觉之可以属仁,而言其当属乎智。至如潘书所言,又因论心性情之分,而以知觉属之心。此所谓各随地头说去者也。且不独潘书然耳,如《中庸序》论人心道心,专以知觉为言,此尤难作智之用看。当时若有人并举此两义问于先生曰:“知觉既为智之用矣,智之用何以能具此理而行此情?智之用何以为人心道心?”云尔。则先生于此,必明有判决,而其所究极同异剖析而会通之者。不但如今日之写在册子上者而已。惜乎!门人弟子无善问者,不能一言及此,而遂成千古未了之案耳。①金昌协指出朱子《仁说》《答胡广仲》②《答吴晦叔》③《答游诚之》④与《语类》⑤等文本,为驳斥湖湘学派“以觉训仁”之说,故将“知觉”只属于“智”,而有知觉为“智之事”“智之用”之说。然而,金昌协认为朱子《答潘谦之》与《中庸章句序》才是朱子论“知觉”的关键性文本。因为,《中庸章句序》言道心人心,紧扣心之知觉而言,而《答潘谦之》则论及“心性分别”。尤其,金昌协非常重视《答潘谦之》,并一度以此书为朱子的“晚年定论”⑥,此书也是金昌协的主要论据,内容如下: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则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者,心也。①
朱子言简意赅地区分心、性、情,并分别“智”与“知觉”。从义理着眼,此书显然是“中和新说”义理间架具体而微的说明。依“心统性情”来说,性与情分属理气、体用,故性为体,其内容只是理,情为用,既是“流出运用处”,则已经属于气。而性与情必须借由“心”的中介,才能使抽象之性理,落实为具体之情。所谓“心之知觉”,亦即“心有知觉”②,知觉是心的主要功能,相对于“性”与“情”,即是心以知觉“具此理”而“行此情”。更精确地说,心以其知觉作用,认知地统摄性而具有之,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之。心之知觉,既是认知的主体,也是行动的主体。因此,就“智,是非之心”的分析来说,“智”是“性”,是“所以知是非之理”;具体的行动是“情”,即“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由静态的是非之理,到动态地表现“分别是非”的行动,就是根据“心”以其知觉作用,认知是非之理而发出道德判断以主宰情而产生“是非之”(是是非非)的行为,此即是朱子“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心也”之义。由此可见,金昌协强调《答潘谦之》之重要性,义理的内在逻辑性大于文本的代表性。③
如此一来,根据朱子思想的逻辑性,若“知觉”仅局限于“智之德”而为“智之用”,则“具此理而行此情”即是“以理具理”,是“头上安头”④,不合乎逻辑,无法解读。因此,金昌协认为朱子虽有“知觉”为“智之用”与“心之用”两种说法,但二者是矛盾的。也许朱子因言说脉络而有不同的说法,所谓“各随地头说去”,但严格地从思想的逻辑性看,“知觉”为“智之用”或“心之用”是不相容的两个命题。可惜朱子弟子并未意识到此问题,否则朱子应该能有会通诸说而有所判决,不致留下此“千古未了之案”。当然,在金昌协看来,会通二者的做法,就是将“智之用”与“心之用”之“用”另加界定。故金昌协说:“盖曰心之用者,专一心之妙用而言也。曰智之用者,偏以智之端绪而言也。智之端绪,则故不能外于心。而若心之妙用,则岂可偏属于智哉?”①言下之意,不仅“智”与“知觉”有偏全之别,“智之用”与“心之用”也有偏全之分。因为知觉属“心之用”之“用”,是指“妙用”“发用”而言,“知觉”内在于心,由心直接发用,必然产生实际的行动,这是“实说”的“用”。即使“仁义礼智”四性,也要有心之“知觉”才能具体化,“知觉”并不偏属于“智之用”。若说知觉属“智之用”,则只能就“智”(性)与“分别是非”(情、心)的对应而言,是“偏以智之端绪而言”。确切地说,由是非之心之端绪,而逆推是非之理,此即是朱子常用的“即情言性”“指心认性”,具体地说,“智”之性(理)不离心之知觉而随事发现。由于“分别是非”之“知觉”(心)与“智”之性(理)是外在的关联,故知觉为“智之用”之“用”,并非意味着“智”(性理)本身能发用,而仅是意味着不可见之“智”(性理)能因心之“知觉”而发现于“情”上。故“智之用”之“用”是“随事发现”之义,亦可说“智之事”②,此“用”本身不具能动性,是“虚说”的“用”。
此外,金昌协还面对李喜朝、玄德润“知觉之何自”的提问,反驳“知觉为智之用”的说法。金昌协说:
夫使知觉而果原于智也,则德久之问而朱子之答之也,何不曰知觉是智之所发,而直以归之于气之虚灵耶?于此审之,则谓知觉为原于智,其是非得失,决矣。③
若依“智”与“知觉”的对应而言,只可以说“智”是“知觉”的所以然之理,这是从存有论的根据来说的,而“知觉”之理仅能对应于“智”。然而金昌协却在朱子《答林德久》得到回应对手的直接答案。朱子面对林德久问“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所有知觉者,自何而发端?”时,他的回答是:“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与形器渣滓正作对也。”①固然从存有论上说,知觉以智为其存在的所以然之理,但从知觉的发生论来看,“知觉”的本质构造是“气之虚灵”,它是气之发用。就此而言,知觉不原于智,当然也不属于“智之用”。
综上所述,不论从心性论或理气论上说,“智”与“知觉”必然要区分。即使言及“智之用”与“心之用”,二者之“用”,意涵也不同,一为间接的“发见”义,一为直接的“发用”(妙用)义。由此可见,金昌协对于朱子心之“知觉”的掌握,以及“知觉为心之用”的论述,实有其独特的见解。
四 金昌协论“心之知觉”
如前所述,金昌协所谓的“知觉”,是“专一心之德”,它已经从偏属于“智之德”中独立出来,指涉心的主要机能。金昌协对此有正面而精辟的分析,笔者归纳为三个要点来说明:
(一)“知觉”“虚灵”“神明”为心之特性
金昌协除辩论“知觉”为“心之用”外,更指出“知觉”是“心”的本色,他晚年所写的《答道以》就表明此义。金昌协说:
盖心有以理言者,有以知觉言者;知觉是其本色,而理则其所具也。此方细论心性情三者界分,故不但曰心,而必著知觉二字,使无混于性耳。然则此二字,正是紧要眼目,岂得为泛论者耶?且心之为心,只是一个知觉,非于知觉外别有心;而亦非于心之知觉外,别有知觉。②
金昌协更进一步以“虚灵”之气来形容“心体”(心之体段):
今试先论虚灵者之为智与否?盖此二字,于古无之,而朱夫子创造,以形容心体者。其著于《中庸序》者,犹是就此心发用处言。至于《大学》注,则专言此心具众理应万事之体用。而直以是蔽之,则其旨益可见矣。……然则心之虚灵,果何为也?盖尝思之:心者无他,气而已矣。专言则聚五行之精英,偏言则属乎火。属乎火,故能光明不昧而照烛万物。聚五行之精英,故能变化无穷,不滞于一方。心之所以虚灵,其理只如此而已。知虚灵之如此,则知觉者。亦可知矣。天下顾安有无理之气哉?而亦何必切切然强属于仁义礼智,然后方免为性外之物哉?①
金昌协认为“心”可从理、气两面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心既是“理”又是“气”,这不合乎朱子理气论的逻辑。因此,就理而言心,只能说“心具众理”,而心本身不是理。如此一来,“心”只能属于“气”,所谓:“心者无他,气而已矣。”但从心、性、情三分来看,“心”必着上“知觉”二字来形容,否则无法与“性”区分(甚至也无法与“情”区分)。言下之意,金昌协似乎认为朱子以“知觉”来界定“心”有严格的意义,不是随意的泛论。换言之,心之为心,“只是一个知觉”。“知觉”是“心”的真正指涉,一言及“心”即指“知觉”,一言及“知觉”必就“心”言。如是,“知觉”成为朱子论心的核心概念。一言以蔽之,知觉是心的本色。这样的说法,虽隐含于朱子思想中,直到金昌协的正面论述,“心之知觉”才成为一个鲜明而重要的性理学概念。
犹有进者,“心”虽属于“气”,但却是独特之气,所谓:“心者,气之精爽。”“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在这个意义下,除了可用“知觉”来指涉心外,也可以用“虚灵”来形容心的面貌与特质(心体)。金昌协甚至认为“虚灵”二字连用来形容心体,是朱子所独创。在《中庸章句序》里,朱子以“心之虚灵知觉者,一而已矣”来说明心的发用。而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则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来解释“明德”。因此,“知觉”“虚灵”二者都指涉“心”,故二者可以连言而为“虚灵知觉”。
同时,金昌协也对心之“虚灵知觉”的特性,做了更具体的描述。他认为心既然是气之灵,故它是“具五行之菁英”,故能变化无穷,妙用无方。如若要将虚灵知觉对应于“智”之德,则从五行而言,虚灵知觉偏于火,其特性是“光明不昧而照烛万理”。换言之,狭义地从“知觉”与“智”的对应而言,“知觉”的特性即是“照”。因此,金昌协在辩论中常使用镜照的比喻说:“智之于是非,固犹鉴之于妍媸。妍媸虽在物,而妍者照其为妍,媸者照其为媸,此非鉴之分别而何?智之为别,正亦如此。”①又说:“夫朱子所谓分别,正亦以知照而言,非有他也。”②在金昌协看来,“智之于是非”如鉴之于妍媸,“智”如明镜高悬,是分别是非底道理,乃不易之则;而物之妍媸,乃分别是非的结果。根据朱子“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③来说,智无运用,因而分别之作用,即在于心之知觉。故鉴之照物,分别即是“照”之作用,故金昌协以镜照喻“知”(知觉),而有“知照”一语,显示“知觉”的特性。
有趣的是,金昌协对于朱子使用“知觉”“虚灵”二字脉络的考察,也精细到锱铢必较的地步。金昌协辨析说:
但此两语,虽非有体用之分,而详味其立言命意,却自有所主。虚灵云者,状其德也(只“虚灵”二字,尽此心体用之德)。知觉云者,指其实也(心之所以为心者,只是一个知觉而已)。是亦略有不同矣。是以朱先生文字中,用此两语,各有攸当,不容差互。如《大学章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答潘谦之》书:“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是皆言心统性情之义。而一则主于解释明字,故以状其德者称之。一则主于分别心性,故以指其实者称之。此皆从分金秤上秤出来。而于前言者,可以见虚灵之兼乎用;于后言者,可以见知觉之兼乎体矣。至于《中庸序》文,专言心之所以为心,则二者并举。以先状其德而后指其实,盖取其备也。而其语意,曰虚灵而能知觉,曰虚灵底知觉云尔。非以二者为有体用之分,而必对举而言之,若云虚灵与知觉也。至其下文,只言知觉而不言虚灵,则亦以人心道心之分,只在于所知所觉、公私之异,故专以是为言。①
金昌协从朱子使用“知觉”与“虚灵”的脉络,指出此二词的立言命意各有不同的重点。“虚灵”出自《大学章句》之注“明明德”,从“虚灵”能“具众理”而言其体,就其能“应万事”而言其用,故“虚灵”是形容“此心体用之德”。至于“知觉”则在《答潘谦之》中有最明确的界定,针对心性之别,是对“心”的实际指涉。换言之,“虚灵”形容“心之德”,“知觉”指涉“心之实”。而最完备的表述则在《中庸章句序》:“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由“虚灵”“知觉”并举而非对举,可知“虚灵知觉”是“心”之特性最完备的表述。
与“知觉”“虚灵”之义相同的,还有“神明”一词。金昌协认为“心之神明”与“虚灵知觉”意涵相同。金昌协说:
《孟子·尽心》章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应万事。”与此“知”字之训大略相同,此非有两个神明也。统言心,则且就人身说其为主宰。专言知,则又就心中说其为妙用。盖心是人身上神明底物事,而其所以神明,只是此个知而已。彼此参互以观,可见此二字,特以状心之妙用而非直说性也。②
金昌协指出“神明”一词出现于《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朱子章句。在此解释脉络下,“神明”可以形容心之妙用,也可以用来形容“知”。因为,一般说心,以心为一身之主宰;说“知”(虚灵知觉),则以其为心之妙用。心之所以神明,就在于“知”。因此,“神明”与“知”(虚灵知觉)可以互换而观,二者都是形容心之妙用。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昌协巧妙地将朱子所言的“知觉”“虚灵”“神明”等词有系统地关联起来,成为说明心之特性的概念。而此说明,又相应于朱子论心的内在逻辑性,将朱子隐而未发之义彰显出来,有其卓见。
(二)心之“虚灵知觉”兼体用、贯动静
虽然在朱子心性理气论中,真正的能活动主体是属于“气之灵”的“心”,但并不意味着“心”只能就动处言,只是发用。因而金昌协以“知觉”“虚灵”“神明”来形容“心”的特性时,也强调“知觉”能兼体用、贯动静,并不只偏于动处或发用时。金昌协说:
窃尝谓心之为物,本无体质方所,而又自神明不测,此“虚灵”二字之所以立,而初非有动静体用之殊者也。今也但见其体之在中者,无形可见。而不知其用之应物者,未始有迹。……况“灵”字之义,不止于静一边,尤明白易见者。今不察此,而并以为此心未发之体,此岂为识虚灵之妙者哉。至于知觉,本亦指此心全体昭昭灵灵者而为言。是虽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方寸之中,固常了然不昧。凡其耳目之聪明,身体之容仪,皆有以主宰管摄而不昏不乱者,皆是物也。今说知觉,专以此心感物而动者言之,则又岂足以尽知觉之义哉?大抵心之虚灵知觉,贯动静而兼体用。虚灵之体,即知觉之存于未发者。虚灵之用,即知觉之见于已发者,非有二也。舜瑞之说,以为虚灵无分于动静,而知觉只可言于动而不可言于静,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是盖以未发时,不容说有知觉,故须著之理二字,而却不知此时虽未有所知所觉,而若其能知能觉者,则未始不了然,何但有其理而已哉?苟有见乎此,则虚灵之不专于静,知觉之不专于动,而不当分属乎体用者,可知矣。①
金昌协针对当时学者对于“知觉”“虚灵”的误解,再度辨明。仅以玄德润(道以)为例,似乎就认为“虚灵”只能形容心之体,“知觉”则指心之用。前者属静时未发之心,后者只动时已发之心。亦即“虚灵”“知觉”分属心自身之体用、动静。不过,金昌协却反对此说法。他认为心之“虚灵”无分于动静(未发已发)、体用,“知觉”亦然。就“虚灵”言,本形容“心之德”(心之特性),因其“具众理”而言体,就其“应万事”而言用。故“虚灵”不能专属于心之静态的描述,就因为心之“虚灵”动静常存,即使人在动时之耳目聪明、身体容仪,依旧是此心之虚灵的主宰。同样地,“知觉”也不偏于心之动态的说明。即使事物未至,思虑未萌之静时,此心仍然“知觉不昧”,只是其作用隐而未显。据此,金昌协指出:未发之时,“知觉”即以“虚灵之体”的样态默存于心而不显;已发之际,“知觉”即以“虚灵之用”的发用而见诸行事。金昌协更以朱子《与吕子约论未发》①《答潘谦之》等文本来证明己说。金昌协说:“如潘书所云‘心之知觉,具此理而行此情’,亦自兼体用说。盖能具此理者,知觉之体也;能行此情者,知觉之用也。其义尤分明矣。”②如此一来,“知觉”之“具此理”言其体,“行此情”言其用;此与“虚灵”之体用义相同。在这个意义下,“虚灵”与“知觉”名异实同,兼体用而贯动静。
此外,金昌协也认为“知觉”也不能因能所之分,而质疑“知觉”之主体性与存有的常存性。金昌协说:
《中庸或问》所云“至静之时,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此虽有能所之分,而其为知觉则一而已矣。盖人心虽有知觉,而其用则因事而见。如知寒暖觉饥饱,寒暖饥饱者,所也;知觉者,能也。非所则能无所著。故知觉之用,必因此等而见。若未有寒暖饥饱之前,则虽有知觉,而亦无自以发用矣,非并与知觉之能而无之也。《或问》所谓“能知觉”“所知觉”,其分盖如此而已。何尝谓“能知觉”者非知觉,而必待有所知觉,然后乃可谓知觉也哉?③金昌协一再强调心之所以为心,就在于“知觉”。虽然在知觉的实际发用中,必然预设“能知觉”“所知觉”或“主体”“客体”的认知格局。然而,金昌协认为“知觉”必然就“能知觉”之“心”而言。尽管“能知觉”之心的发用必须见诸所知觉之对象(客体),但即使未有所知觉之对象(客体)之前,“能知觉”之作用仍然默存于心。从“知寒暖饥饱”之例可以得知,吾人并不会因未出现“寒暖饥饱”(所知觉)之现象,就否认心没有“能知觉”的能力。同样地,未发至静之时,心之知觉能具众理,虽未见诸情,但心仍未失其“能知觉”之特性。再者,根据朱子“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的能所区分,“具是非之理”的“心”与“所以是非之理”的“性”有所区别。若必须预设“能知觉”“所知觉”才能独立说“知觉”之义,无疑将“知觉”之心窄化到动时发用,反而无彰显心之“知觉”兼体用、贯动静之特性,而“知觉”为“能知觉”之主体义也将减杀。
(三)“知觉”与“情”的区分与关联
从金昌协对于“智”与“知觉”的区分中,显示朱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别”“理气”之分。但从“心统性情”的架构中,我们还可以追问“心”与“情”的区分及其关联。这一区分朱子除了零星比喻式的说明外,并未详加说明,而金昌协在论及心之知觉时,便分析“知觉”与“情”的区分与关联。金昌协说:
知觉,乃是人心全体妙用,昭昭灵灵,不昏不昧,通寂感而主性情者也。本不当专以就动处与情相比较。而今且以动一边言之,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①
又说:
鄙说“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此正是离合说。……今只请详味“非知觉则无以为情”一句,自见其宾主对待,不容混合为一。所谓“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亦曰知觉之用只于情上见之,此外更无别涂见得知觉作用处云耳,非便以情为知觉也。若于此二句分明看破,则自无疑于会动是知觉之说。盖人只为有一个觉,故事至物来,自会感动。若其如木石之无知觉,则虽事物来触而顽然不动,不动则又安有所谓情哉?然则动固是情也,而其所以能动者,非知觉而何哉?此恐无可疑者。①
这两段话以两个要点说明“知觉”与“情”的区分与关联。一是: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一是:会动底是知觉,动底是情。在朱子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的架构中,性是理,心与情俱属于气。因而,心、性之别是理气之分,亦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性、情分属体、用,也是理气上下之分。然而同属于形下之气的心(知觉)与情,要如何区分呢?从动静来说,前已述及,心之“知觉”无动静之分,无论动时、静时,心都“知觉不昧”。不过,“知觉”与“情”的关联,只就“动一边”而言。一般而言,所谓“情”是指“感物而动”。但“感物而动”的主体是“心”而非“情”,亦即由于心之感物,才引发情之活动。就此而言,心之知觉为主,情为客,二者有宾主之分,故金昌协说“非知觉则无以为情”,知觉是形成情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但知觉在动时的发用,不能隐而不显,必须落实在情之动上显现,除此之外,别无作用之处,此即金昌协所言“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因此,在动的层面、气的层面上说,金昌协所谓“非知觉则无以为情”意味着知觉与情之“不杂”关系,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则显示知觉与情之“不离”关系。
显然,知觉与情这种同质的“不离不杂”,与心性、性情而言的异质之“不离不杂”关系不同,由此可进至“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的讨论。金昌协之语比照朱子所言“动处是心,动底是性”②而来,名言虽同,所指不同。朱子所谓“动处是心,动底是性”,并非意味着“心”与“性”皆能动,而是指能动的、会动的是心,而心之能动、会动的所以然之理是“性”。故“动底是性”之“动底”,不能拘泥于字面的文义理解,误以为“动的是性”,而是要从朱子思想的逻辑性来理解,指的是使“动”成为可能的是“性”,性是动之理,而非动自身。朱子比喻说:“若以谷譬之,谷便是心,那为粟、为菽、为禾、为稻底,便是性。”③从此譬喻可以得知朱子“动处是心,动底是性”之实义。不过,金昌协提出“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时,难免会让人误解,以为“动底是情”与朱子“动底是性”的意涵相同。事实上,从金昌协强调性只是理,发用的是气(心)来看,金昌协不应会误解朱子之义。故金昌协“动底是情”与朱子“动底是性”二者所指不同,不能混合为一。①金昌协“动底是情”之“动底”是就字面意义来说,即是朱子常说的“动底物事”②“动底意思”③。用现代汉语说,“动底是情,会动底是知觉”之“底”字与“的”字相通,故金昌协之语即是:“动的是情,会动的是知觉。”此义不难理解,意味着:活动的是情,会活动的是知觉。更准确地说,“知觉”是能动的主体,有活动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活动就是“情”。犹如“目”(眼)之“视觉”之于“视”(看),目之所以为目,即在于目有视的能力(视觉),此视觉能力乃成就视之活动。知觉与情之“不离不杂”由此可以索解。
金昌协上述的说法,字面上虽有些缴绕,但义理的脉络却是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知觉”与“情”之“不离不杂”的关系,与理气不同,金昌协之弟金昌翕就说:
性情之分也则其势一串,心情之判也则势有横直。然则性情之界,上下也,非经纬也。心情之际,经纬也,非上下也。性情之分,言之似易。而心情之析,勘得较难。④
金昌翕认为“心情之判”比“性情之分”更难说清楚,同时也指出“性情之分”与“心情之判”不同,性情是理气之分,故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超越区分。但“心情之判”不是理气之别,二者同属于气而彼此交错,故以“经纬”关系喻之。事实上,朝鲜性理学中首先使用“经纬说”来理解朱子思想的是被归属于退溪学派的张显光(字德晦,号旅轩,1554—1637)。他在《性理说》中阐发“理气经纬说”。其实,“经纬”是一种譬喻,根据张显光的解释:“经即织缕之纵而在柚者也,纬即织丝之横而在杼者也。经则自始至终,通贯直达而无有变易;纬则一左一右,反复往来,而须备曲折。”①据此,他在论“在人经纬”时,也提出了“性情经纬”说。金昌协曾运用此譬喻,也指出:“盖性为经,而情为纬,错综迭为体用。须如此看,方为活络,且似周尽。”②情之为用,变化万端;性之为体,其理恒定。二者交迭,不离不杂。而金昌翕也将金昌协的心情关系以“经纬”喻之,亦即“知觉”为经,“情”为纬,因为在情的多样变化中,皆是一心之“知觉”的发用。这样的譬喻,金昌协虽未用于“知觉”与“情”的分析,但从其思想的逻辑性来看,应能接受其弟的诠释,此种诠释也呈现朝鲜性理学独有的特色。
五 结语
朝鲜后期性理学的“知觉论争”,由宋时烈启其端,继而由金昌协正式将此论题主题化(thematize),提出“知觉”为“心之用”的论据,由此引发朝鲜性理学者的关注,直至韩元震仍以“知觉”是“智之用”与之激辩。在金昌协之前的朝鲜性理学者,并未对朱子思想中“智”与“知觉”所隐含的哲学问题加以思考,而金昌协将此论题提至哲学高度来探究,有其卓见。金昌协认为不论从朱子心性论或理气论来深究,“智”为性、为理,“知觉”为心、为气的区分不容含混。换言之,“智”与“知觉”之辨,即是心性理气之辨。在此问题意识下,金昌协指出朱子言“智”只限于五性(仁义礼智性)之一,但朱子言“知觉”则专属“一心之德”,“知觉”并非只是与“智”对应配属的“智之德”而已,而是心之所以为心的本色与特性。金昌协也能掌握朱子“性只是理”与李栗谷“气发理乘一途说”之义,在区分“智”与“知觉”之际,指出真正能发用的是气,是知觉,故“知觉”不是“智之用”而是“心之用”。
更重要的是,在论证上,金昌协以朱子《答潘谦之》为文本根据,“中和新说”之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为义理间架,证成心之“知觉”能“具此理”而“行此情”,统摄性与情而成为朱子论心的重要概念。金昌协不仅以“知觉”来界定“心”的特性,还认为“虚灵”“神明”亦能形容心之特性。在金昌协看来,“虚灵知觉”最能彰显心之特性,它兼体用而贯动静。犹有进者,金昌协还进一步辨析“知觉”与“情”的关系,从动时、气的层面指出:“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其弟金昌翕还以“经纬”的交错迭用,解释心(知觉)与情的不离不杂。此种辨析与思路,并未见于中国朱子学的思维架构,但却早已出现在朝鲜性理学“四端七情”的论述中,颇具朝鲜性理学的特色。
不过如同“四端七情”所引发的“道德情感”(四端)与“一般情感”(七情)的异同,从哲学反思来说,金昌协以“知觉”为“心”的主要作用,则心之“知觉”,是否有对“道德法则”“自然法则”与“感官”的异质区分?朱子与金昌协似乎未意识到此问题。在这个意义下,“知觉”是属于“智之用”或“心之用”,也涉及“理发”或“气发”的根本问题,或是道德意识的成立问题。这样的提问,以不同的讨论类型,出现在朱子学、阳明学与朝鲜性理学的论述中,甚至涉及儒、释之辨。①且从东亚儒学的视域来看,相较于朝鲜后期的“人物性同异论”论争,“知觉”论争反而是一跨文化的哲学论题,亟待深究。
附注
①韩国学者문석윤(文锡胤)将朝鲜后期重要论争梳理为“四端七情论辩”“太极论辩”“知觉论辩”“未发论辩”“人物性同异论辩”,既有宏观的统摄,又有微观的分析,值得参考。参见氏著:《조선후기의주요논쟁과쟁검》(《朝鲜后期的主要论争与争点》),한국국학진흥원국학연구실(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室)编:《韩国儒家思想大系》第3册《哲学思想编》(下),경북:한국국학진흥원,2005年,第293-384页。另参见氏著:《朝鲜湖洛论辩中知觉论的意义——儒教的道德实践与知识问题》,《韩国学论文集》第7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1998年,第260—265页。
①参见李丙春:《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第201—203页。
②参见高桥亨:《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田保桥洁编:《京城法文学会第二部论集》,东京:刀江书院,1929年,第267—281页。
③宋时烈:《宋子大全》Ⅴ,卷131,《看书杂录》,第3a页,《韩国文集丛刊》第11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第42页。本文凡引《韩国文集丛刊》之文集,除首次标明辑数外,其总页数直接以/下标示。
①《宋子大全》Ⅴ,卷131,《看书杂录》,第5a/429页。
②朱子于《孟子·万章上》伊尹所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批注云:“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
③朱子《答吴晦叔》第10书云:“若夫知觉,则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四,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1829页)
①金昌协:《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1书,第1a页,《韩国文集丛刊》第16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4页。
②高丽末朱子学东传时,胡炳文《四书通》是丽末鲜初儒者理解朱子学的重要凭借,被尊称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号圃隐,1337—1392)就因为其讲解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与后来东传的《四书通》吻合,而令诸儒叹服。《郑梦周传》载云:“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郑麟趾等纂修:《高丽史》卷117,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册,第442页)
③《农岩集》Ⅱ之卷14中有《答闵彦晖》书共六封,第1封写于丁丑年(1697),故《年谱》载两人辩难“书至六、七度”。参见《农岩集》Ⅱ,卷36,第14a/425页。
④《农岩集》Ⅱ,卷36,《年谱》,第14a/425页。
⑤李喜朝《芝村集》卷8中有写于乙酉年(1705)年的《答金仲和书》,《韩国文集丛刊》第17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而金昌协《农岩集》卷13中有写于丙戌年(1706)的《与李同甫书》。
⑥《农岩集》中有《答道以》书共四封,最后一封写于丁亥年(1707),参见《农岩集》卷19。
①金昌协“知觉”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김태년(金太年):《洛論系의知覺論연구》(《洛论系的知觉论研究》)(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此论文通过知觉研究的展开过程来看朝鲜朱子学者如何吸收阳明学的问题意识。而氏著:《지각》(《知觉》),也专章收入한국사상연구회(韩国思想研究会)编:《조선유학의개념들》(《朝鲜儒学的概念》),首尔:예문서원(艺文书院),2006年,第299—321页。又조남호(赵南浩):《金昌協學派의陽明學批判:智와知覺의문제를중심으로》(《金昌协学派的阳明学批判:以智与知觉为中心》),한국철학희(韩国哲学会):《철학》(《哲学》)第39辑,1993年,此文从朴世堂的批判过程中,探讨其对王阳明至少论有关知觉的批判;而氏著:《羅欽順의철학과조선학자들의논변》(《罗钦顺的哲学与朝鲜学者的论辩》),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5章,特别讨论金昌协与韩元震有关智与知觉的论辩。又문석윤(文锡胤):《朝鮮後期湖洛論辨의成立史》(《朝鲜后期湖洛论辩的成立史》),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从与湖学对·比的洛学心性论来鸟瞰知觉研究。又김현(金炫):《조선후기未發心論의心學的전개》(《朝鲜后期未发心论的心学开展》),《민족문화연구》第37辑,2002年,其知觉研究是从重视心的侧面来检讨阳明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关联性。又이천숭(李天承):《農巖金昌協의知覺論議와心의의미》(《农岩金昌协的知觉论议与心的意义》),《韩国思想史学》第21辑,2003年,此文以金昌协为中心,考察洛学系学者从现实问题中对作为朱子学运作原理的知觉论议所具有的作用。更详细的研究,亦参见氏著:《농암김창협의철학사상연구》(《农岩金昌协的哲学思想研究》),第4章,경기도:한국학술정보(京畿道:韩国学术情报),2006年。笔者则着重从朱子思想的内在脉络,探讨金昌协如何论述“智与知觉”这个论题。
①牟宗三指出:中和问题之参究与仁之问题之论辩是朱子思想奋斗建立之过程;并分析出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是“中和新说”的义理格局。参见氏著:《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第353、144页。
②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世界书局,1984年,第168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5—956页。二书皆将《中庸章句序》系于淳熙十六(己酉)年,朱子六十岁。但钱穆经细加考证,指出:“《中庸章句序》成于淳熙己酉,越两年辛亥,答蔡季通贻书,憾语有未莹。《答(郑)子上书》又曰:《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今读《中庸序》与《答(郑)子上书》意同,则已是改定之本。人心道心之辨,盖至是始臻定论。”如此一来,《中庸章句序》之定稿,当在绍熙二年(辛亥),朱子六十二岁。参见氏著:《朱子新学案》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第113页。
③蔡茂松认为朱子论知觉以《中庸章句序》为定论,并以此分为前后两期,详加辨析论述。前期在《中庸章句序》之前,尤以四十五岁前后与张南轩等湖湘学派,以及反对谢上蔡“以觉训仁”为主要内容;后期以六十岁以后《文集》《中庸章句序》《答潘谦之》《答余方叔》,以及《语类》僩录、节录、淳录等所记录知觉之说为重要内容。参见氏著:《朱子学》,台南:大千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409—448页。本文对朱子知觉说的探究,不从前后期着眼,而以义理问题为论述主轴。
①《已发未发说》见于《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1书见于《朱子文集》卷六十四,《答张敬夫》为第18书,见于《朱子文集》卷三十二。
②《朱子文集》卷六十四《已发未发说》,第3377页。
③《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第18书,第1273页。
④同上。
①《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卷五,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94页。
②朱子云:“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同上,第90页)
③朱子云:“心统性情,故言心之体用,尝跨过两头未发、已发处说。”(同上,第94页)
④朱子云:“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同上,第96页)
⑤朱子云:“心者,气之精爽。”(同上,第85页)
⑥朱子云:“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同上,第85页)
⑦朱子云:“虚明不昧,便是心……感物而动,便是情。”(同上,第94—95页)
⑧朱子《问张敬夫》第6书:“情根乎性而宰乎心……中节、不中节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以明矣。”(《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第1245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第474页。又说:“心之统摄性是主观地认知地统,心之统摄情是客观地行为地(激发地)统。”(同上,第378页)
②李明辉以“表象力”来翻译朱子的“知觉”,既相应于朱子的用法,也可以避免朱子“知觉”一词在概念上所引起的误解。参见氏著:《朱子论恶之根源》,锤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574页。韩国学者김태년(金太年)虽以,perception"翻译"知觉”,但也注意到(朝鲜)儒学所谓的快^”包含感官知觉与认知道德原理。他指出:人把握世界内在的道德秩序,并在自己身上实践的能力为何?这种作用的机制为何?讨论这些问题便是儒学的知觉论。与西洋的知识传统相比,儒学注重的是道德上的“是、非”,更甚于认知上的“真、伪”。更正确地说,“是”即是“真”,“非”即是“伪”。并认为“理”是知觉的对象,“心”是知觉的主体,"情”则是知觉显现的结果。朝鲜儒者对于心、性、情关系的说明,各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此差异也影响到修养论的不同。参见氏著:《지각》(《知觉》),《조선유학의개념들》(《韩国儒学的概念》),第299-301页。
③《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①朱子云:“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语类》卷六十二,第1478页)
②《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仁说》,第3390—3391页。
③参见李明辉:《朱子的“仁说”及其与湖湘学派的辩论》,氏著:《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88页。
①朱子《元亨利贞说》:“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朱子文集》卷六十七,第3361页)
②《朱子文集》卷七十四《玉山讲义》,第3733页。
③同上,第3734页。
①《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陈器之ニ问〈玉山讲义〉》,第2827页。
②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者山崎闇斋(1618—1682)阐发此义,而有“智藏说”。相关研究参见冈田武彥:《朱子と智藏》《朱子の智藏說とその由來および繼承》,氏著:《中國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現實》,东京:木耳社,1983年,第267—279、280—304页;亦参见氏著:《山崎闇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对朱子智藏说的宣扬》,第125—136页。亦参见难波征男:《日本朱子学与将来世代——智藏论》,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3—411页。本文暂不探究此论题。
①《语类》卷五十三,第1290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第280页。
③《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仁说》,第3392页。
④《朱子文集》卷三十二《又论仁说》第14书,第1226页。
①朱子云:“佛氏元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如视听言貌,圣人则视有视之理,听有听之理,言有言之理,动有动之理,思有思之理。……佛氏则只认那能视、能听、能言、能思、能动底,便是性。视明也得,不明也得;听聪也得,不聪也得;言从也得,不从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横来竖来,它都认做性。它最怕人说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语类》卷一百二十六,第3020页)
①《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1书,第2b/4页。
①《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1书,第2a—b/4页。
②《大学或问》上:“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欲勉强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先必有以致其知。”(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③《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
④同上,第349页。
⑤《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2书,第8b/7页。
①《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3书,第10a/8页。
②《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5书,第25a/16页。
③《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4书,第12a/12页。
④《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1书,第2a/4页。
①《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丙戌,第37a—b,《韩国文集丛刊》第161册,第562页。
②《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1书,第4a/5页。
①《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4书,第19b/13页。
②《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5书,第26b/16页。
③《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4书,第22b—23a/14—15页。
④同上,第20a/13页。
①《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丙戌,第38a—b/562页。
②朱子云:“盖孟子之言‘知觉’,谓知此事、觉此理,乃学之至而知之尽也。上蔡之言‘知觉’,谓识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智)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大体皆智之事。”(《朱子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第5书,第1812页)
③朱子云:“若夫知觉,则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觉,而不可便以知觉名仁也。”(《朱子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第10书,第1829页)
④朱子云:“若以名义言之,则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知(智)之用。界分脉络自不相关,但仁统四德,故人仁则无不觉耳。”(《朱子文集》卷四十五《答游诚之》第1书,第1996页)
⑤朱子云:“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觉者乎?”(《语类》卷六,第118页)
⑥金昌协1697年的《答闵彦晖》第一书,认为朱子《答潘谦之》书“此说于心性之辨极其精微,铢分粒剖,更无去处,殆是晚年定论”(参见《农岩集》Ⅱ,卷14,第3b/5页)。但经辩论后,金昌协1704年的《答道以》、1706年的《与李同甫》中的看法已经有所松动。
①《朱子文集》卷五十五《答潘谦之书》第1书,第2607页。
②金昌协《答道以》甲申云:“盖曰心有知觉,则谓心之知觉,固当矣。”(《农岩集》Ⅱ,卷19,第3b/5页)
③如金昌协《与李同甫》云:“潘书与诸说诚难定其孰为先后,然其义终难会通为一,故或疑有初晚之异,是亦不得已焉耳。”(参见《农岩集》Ⅰ,卷13,第35b/561页)由此可见,金昌协坚持以《答潘谦之》为论证的文本根据,实际上是基于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性,即此书与“中和新说”的义理间架若合符节。
④金昌协《与李同甫》云:“且智即性也、理也,而今曰智之体能具此理,则是以理具理也,庸非所谓头上安头者乎?”(《农岩集》Ⅰ,卷13,第36b/561页)
①《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第39b—40a/563页。
②金昌协《答闵彦晖》第4书云:“今且以智言之,分别是非正是智之实事。”(《农岩集》Ⅱ,卷14,第18b/12页)
③《农岩集》Ⅱ,卷19,《答道以》己卯,第20b/102页。
①《朱子文集》卷六十一,第3016页。
②《农岩集》Ⅱ,卷19,《答道以》甲申,第29a—b/106页。
①《农岩集》Ⅱ,卷19,《答道以》己卯,第20b—2la/101—102页。
①《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1书,第4a—b/5页。
②《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2书,第8a—b/7页。
③《朱子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第5书,第2025页。
①《农岩集》Ⅱ,卷19,《答道以》丁亥,第32a—b/107页。
②《农岩集》Ⅱ,卷14,《答闵彦晖》第3书,第15a—b/11页。
①《农岩集》Ⅱ,卷19,《答道以》丁亥,第31a—32a/107页。
①朱子《答吕子约》第11书云:“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虽未发而未尝无。心之有思,乃与耳之有听,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一有此则不得为未发。”(参见《朱子文集》卷四十八,第2182页)据此,金昌协《与李同甫》云:“如与吕子约论未发书,以心之有知与心之有思分别言之,不翅明白。可见此心未发,固自有知觉矣。”(《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第30a/559页)
②《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第30a/559页。
③同上,第33b—34a/560页。
①《农岩集》Ⅱ,卷19,《与道以》甲申,第28b/105页。
①《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丙戌,第31a—32a/559页。
②《语类》:问心之动、性之动。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卷五,第88页)
③同上,第91页。
①金昌协《与李同甫》云:“‘动底是情’,虽若异于朱子‘动底是性’之说,其实亦不相妨。朱子之言就动上分心与性,故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此则就动上分知觉与情,故曰:‘会动是知觉,动底是情。’此等要须就实处体认,而嘿会其大意。见其名言虽同,而不害其所指之殊。所指虽殊,而又不害其理之同。然后方为活络,正不当滞泥于文句之间也。”(《农岩集》Ⅰ,卷13,《与李同甫》丙戌,第32a/559页)
②朱子云:“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语类》卷五,第86页)。又:“盖礼是个限定裁节,粲然有文底物事;乐是和动底物事,自当如此分。”(《语类》卷十七,第374页)
③朱子云:“某尝问伯恭来,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据某所见,伊川之说只是非礼勿视听言动底意思。”(《语类》卷七十三,第1857页)
④金昌翕:《三渊集》Ⅰ,卷25,《论智字说》,第23a页,《韩国文集丛刊》第16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519页。
①张显光:《性理说》卷4《经纬说·论经纬可以喻理气》,第1b—2a页,《旅轩先生全书》下卷,仁同张氏南山派宗亲会1982年刊本,第76页。
②《农岩集》Ⅱ,《农岩续集》卷下《四端七情说》,第67b/518页。
①阳明逝世后,其弟子聂双江屡屡抨击王龙溪(名畿,1498—1573)的“见在良知”是“以知觉为良知”,王龙溪、欧阳南野乃与聂双江辩论,展开阳明学脉络下“良知与知觉”论辩,详参拙著:《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486—515页;又明代朱子学者罗整庵也驳斥阳明的“良知即天理”之说,主张“良知即知觉而非天理”,阳明弟子欧阳南野代师反驳之,强调“良知即天理而非知觉”,此为阳明学与朱子学交锋下的“良知与知觉”论辩,详参拙文:《良知与知觉:析论罗整庵与欧阳南野的论辩》,《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第287—317页。而明末云栖袾宏(1535—1615)也不得不划清界限,指出阳明之“良知”并非佛说之“真知”,参见氏著:《竹窗随笔·初笔·良知》,《大藏经补编》第23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1986年,第26b—27a页。又朝鲜性理学的“智与知觉”论辩,则源自朱子学内部的脉络,也与罗整庵对阳明学的批判相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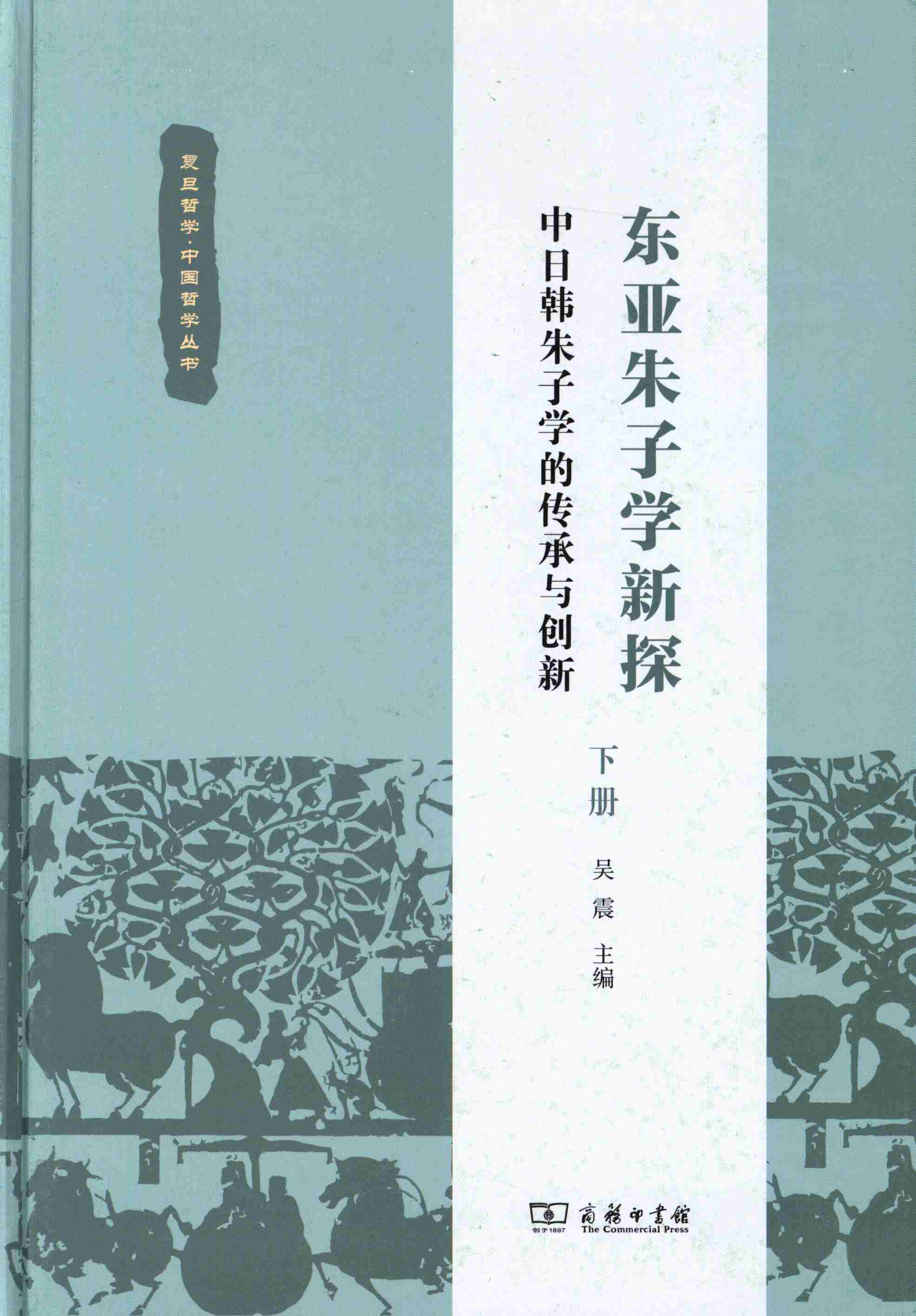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下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
阅读
相关人物
林月惠
责任者